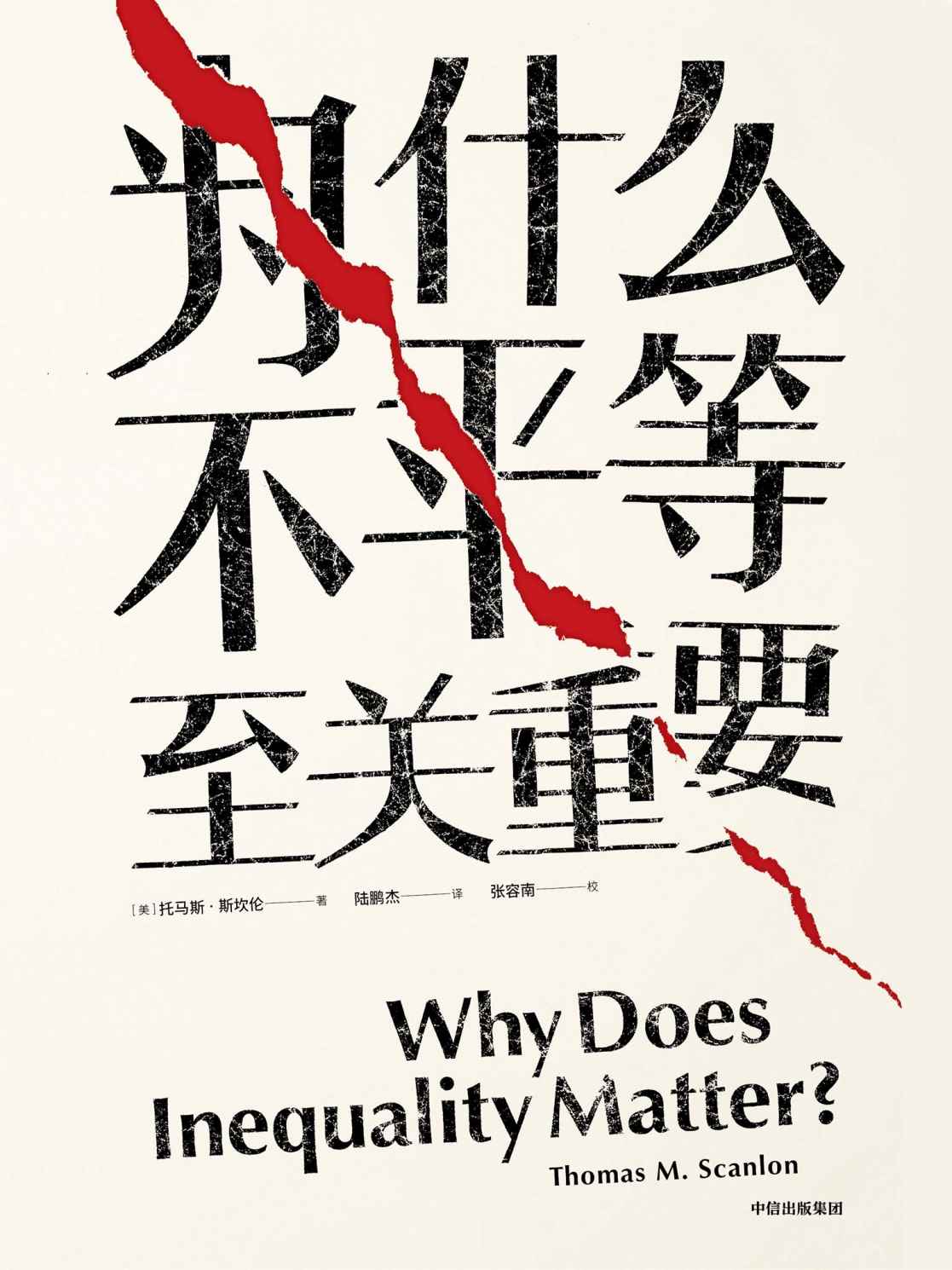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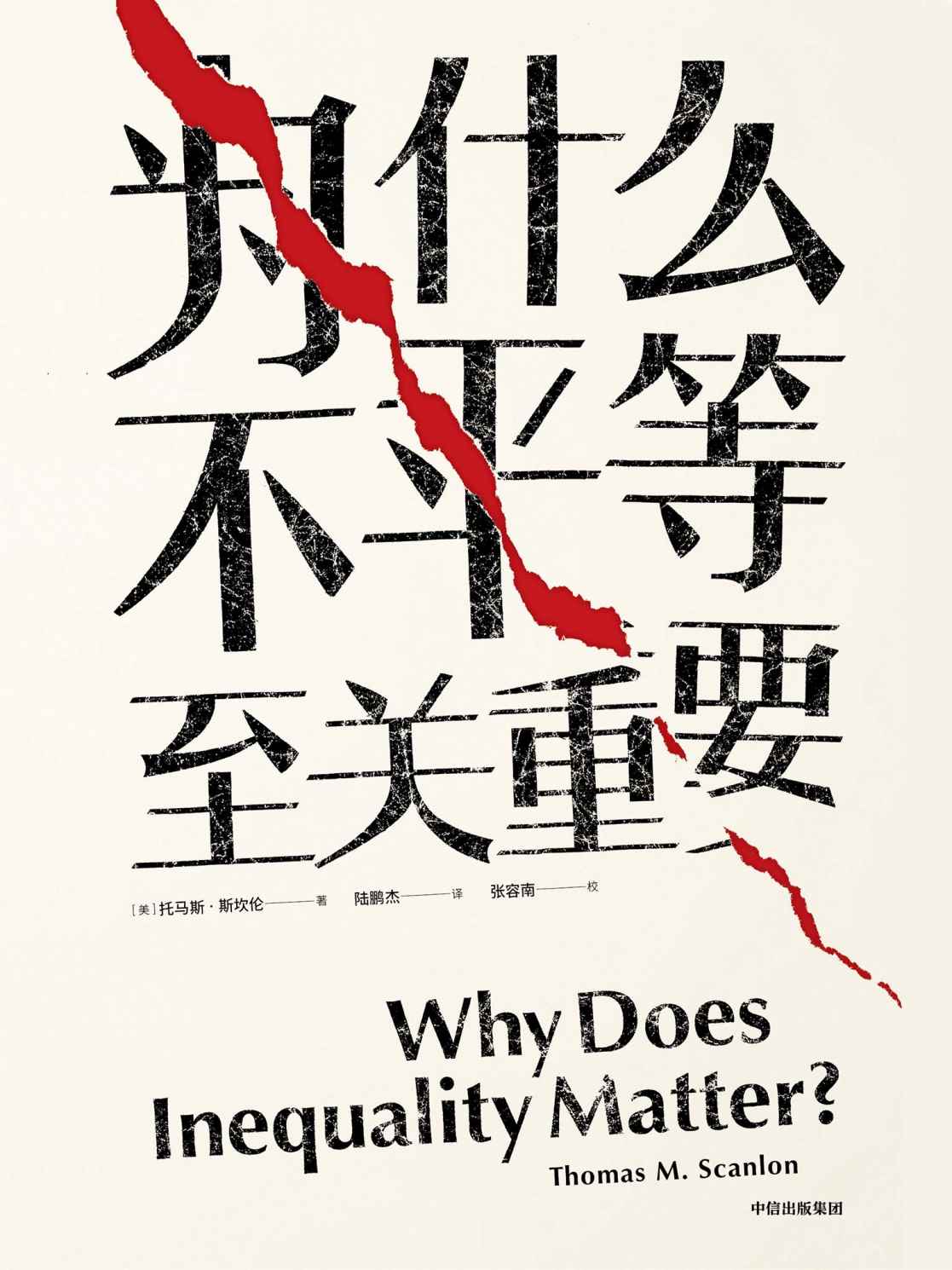
献给杰西(Jessie)和萨拉(Sarah)
本书是我的尤希罗讲座(Uehiro Lectures)的扩展修订版,我曾于2013年12月在牛津担任过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要感谢朱利安·萨伏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尤希罗基金会邀请我发表演讲,并感谢我当时的评论人——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和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给出了深刻的评论。
呈现在这里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Lindley Lecture),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次讲座的内容后来发展成了一篇以《平等何时重要?》作为题目的论文,并且我把那篇变得越来越长的论文展示给了更多的听众,多到我无法把他们列举出来。我从那些场合中收到了许多评论和建议,它们都让我受益匪浅。尤希罗讲座的邀请提供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激励,它促使我将那篇未完成的论文扩展成三次演讲,而那些演讲的内容现在又被扩展成十个章节。
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许多人给了我宝贵的帮助。以下诸君为我草稿中的某些章节,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整本书的草稿,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约瑟夫·费希金(Joseph Fishkin)、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尼科·克洛德尼(Niko Kolodny)、马丁·奥尼尔(Martin O’ Neill)、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汤米·谢尔比(Tommie Shelby)、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曼纽尔·瓦尔加斯(Manuel Vargas)和保罗·威特曼(Paul Weithman)。此外,我收到的另一些犀利而富有启发的评论,则来自2016年春季学期我的政治哲学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和杰德·卢因森(Jed Lewinsohn)。我衷心感谢他们。拥有如此慷慨大方且让人受益的朋友和同事,真是太美妙了。我也要感谢理查德·德·费利皮(Richard de Filippi)跟我讨论了人们在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和健康状况上的不平等,并感谢诺尔·多明格斯(Noel Dominguez)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辅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露西(Lucy)的支持。此外,在吃早餐和晚餐的时候,我曾反复尝试向她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不平等是一个如此难以著述的议题,我还要感谢她对我做出了深思熟虑且富有耐心的回应。
目前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盛行着某种极其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道德上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我们并不清楚究竟为何会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清楚,反对不平等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减少或消除不平等的道德理由是什么。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理解这些理由。
我们也许会想把资源从富人手中再分配给穷人。支持这种想法的一个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让穷人过得更好,而对富人的福祉造成的代价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支持再分配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在反对不平等 ;也就是说,这不是在反对某些人的幸福水平与另一些人的幸福水平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仅仅是一个支持提高穷人的幸福水平的理由,也许还是非常强有力的理由。有些人比穷人过得好得多,这一事实之所以和支持再分配的这个理由有关,仅仅是因为,正如美国著名的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在被问及为何抢劫银行时说的那样——“钱就在那儿”。
相比之下,某些理由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理由,就在于它们反对某些人的拥有物与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它们要求缩小这种差异。接下来,我将特别关注这类理由。但这不是因为这类理由比改善穷人命运的理由更重要(它们往往不会更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更令人费解。
我们似乎很难证成(justify) [1] 对平等的关注。例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指责。他认为对平等的关注是对特定分配模式的关注,而且这种模式只能通过干涉个人做出选择、承担风险和签订契约的自由来维持,因为这些自由会扰乱这种模式。 [2] 诺齐克问道,为什么我们要以不断干涉个人自由为代价去试图维持一种任意的分配模式呢?
当我们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来表明平等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冲突时,平等似乎立即处于劣势。人们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反对干涉自由:任何人都不希望别人夺走他 [3] 珍视的那些选项,也不希望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但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则没那么清楚。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去关注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之间的差异呢?因此,人们常常指责说,要求更大程度的平等不过体现了“穷人”对“富人”的嫉妒。
平等主义(即关注平等和不平等)的理由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而言,只要某些理由反对一些人的拥有物和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它们就是平等主义的理由。这包括那些以这种差异的后果作为依据的理由,即便那些反对后果的理由与平等无关。例如,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平等会对穷人的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4] 这无疑为减少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性理由。这些理由虽然在广义上是平等主义的理由,但在狭义上却不是如此,因为关注不健康的理由本身并不是平等主义的理由。从狭义上而言,如果某些理由最终所依据的观念是为什么平等本身值得追求或者为什么不平等本身应被反对(objectionable) [5] ,那么它们才是平等主义的理由。反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它会让富人对穷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控制权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被支配者和支配者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反驳在狭义上和广义上就都属于平等主义的反驳。但如果对被控制的反驳只是基于它会导致某些机会的丧失,那么这种反驳就只是广义上的平等主义反驳。
当诺齐克指责对平等的关注是对维持某种分配模式的关注时,他的这种指责主要对狭义的平等主义理由构成了挑战。但基于嫉妒的反驳则质疑人们到底 是否有任何好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无论这些理由是否属于狭义的平等主义理由。
只要支持减少不平等的理由在广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即只要它反对某些人的拥有物和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 ,那么它看起来就会支持减少这种差异,即便这种做法没有让任何人过得更好,并且还导致一些人(富人)过得更糟。这种做法所体现出来的显见非理性(irrationality)构成了所谓的“向下拉平反驳”(leveling down objection)的依据。这个反驳被看作是一种拒斥平等主义而赞成优先主义(prioritarianism)的理由,因为按照优先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只关注改善穷人的处境,而不是关注贫富差距。 [6]
要评估这些挑战,我们就得清楚地解释,人们有哪些理由来关心平等和不平等。此外,为了理解促进不平等的法律和制度到底错在哪里,以及理解改变这些制度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如何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同样也需要这类解释。即使穷人过得更好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贫富差距的缩小会是一件好事,但通过再分配来实现这些目标却仍然可能是错误的。威利·萨顿毕竟是一个强盗,罗宾汉也是如此,尽管后者的动机比前者的动机好。
我认为,存在一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事实上有若干不同的理由会如此。本书的任务便是对这些理由的本质进行考察。我把这一任务描述为考察反对不平等的理由,而不是考察支持平等的理由。因为这种表述方式潜在地包含了更广泛的考量,并不是所有这些考量都在狭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不平等的一些最强有力的反驳与不平等的后果有关,而且并非所有这些反驳都基于平等的价值。
认识到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具有多样性是重要的,因为这也有助于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不平等在种类上的差异。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一回事;过着舒适小康生活的人和赤贫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是另一回事。种族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不同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不平等也是如此。这些不同形式的不平等会面临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由我将描述的那些道德反驳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
我将预设一个重要的平等观念,但不会为它提供论证。这个观念也许可以被称为“基本的道德平等”,即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无论他们在种族、性别和居住地等方面会有哪些差异。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基本的道德平等这个观念,并扩大了它所涵盖的人员范围,这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进步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基本的道德平等目前被广泛地接受,即使在那些拒斥实质性的平等主义主张的人之中也是如此。例如,诺齐克就接受基本的道德平等。当他写道“个体拥有权利”时,他指的是所有的 个体。 [7] 但他否认,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应当使人们在财富、收入或任何其他方面的状况与另一些人的状况保持平等。正是后面这种实质性的平等才是本书关注的对象。我的问题是:一些人在某些方面过得比其他人更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应当在道德上受到反对呢?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确定几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其中的许多理由会在后面的章节得到更详细的讨论。
地位: 就应被反对的不平等而言,历史上最重要的例子是种姓制度和其他在地位上带有羞辱性差异的社会安排。在这些制度中,某些群体的成员被视为低人一等(inferior)。那些被认为最值得向往的社会职务和职业都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甚至被贬低去从事某些职业,这些职业被视为有损人格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尊严。这些安排所涉及的罪恶具有一个比较性的特征:我们所反对的是以一种有损人格的方式把某些人视作低人一等 。因此,这种反驳的核心观念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
在我提到的那些历史案例中,基于种姓、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都是法律问题或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态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态度涉及这类广泛的共同信念,即某些种族的成员没有充分的道德地位,甚至他们可能“不是完整的人”,从而否定了我刚才所说的“基本的道德平等”。但这些信念对于我所关注的反驳来说并不重要。我认为,19世纪英国的阶级制度并没有涉及这些观念,即下层阶级的成员不是完整的人或他们的遭遇在道德上无关紧要,而只涉及他们不适合或没资格担任某些社会职务和政治职务。
基于我现在正在讨论的理由,经济不平等也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可能意味着,穷人必须以一种被合理地视为令人羞辱的方式来生活。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如果在某个社会中,有些人比其他人穷得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着装方式使得他们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感到羞耻,那么这种情况便构成了对该社会的严厉反驳。 [8] 同样的,这里的罪恶也是比较性的——它不在于某些人的衣衫褴褛或住房简陋,而在于这些人用以度日和展示自己的方式只能远远地低于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并且这种方式给他们贴上了“低人一等”的标签。正如“普遍接受的标准”这一短语所表明的,只有当人们对一个人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会被社会接受这个问题持有某种普遍流行的态度时,经济不平等才会产生这些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反对的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规范的某种结合。我会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这种不平等。
控制: 不平等之所以会遭到反对,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让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例如,如果一小部分人控制着一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财富,那么这可能会让他们对其他人的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可购买的物品以及广泛的生活面貌都拥有一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更具体而言,如果一些人拥有国家重要公共媒体的所有权,那么这些人可能就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如何理解他们的社会拥有某种不正当的控制权。我会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九章来讨论对这两种控制形式的反驳。 [9]
机会平等: 当家庭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时,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上的成功前景就会受到出生家庭的极大影响。这可能使得在经济上实现机会平等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人们普遍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很少讨论支持机会平等的理由。我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来考察这些理由以及它们对不平等的影响。
政治公平: 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可能会破坏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响政治讨论的过程,也更有能力为自己谋得政治职位以及影响其他的公职人员。这可以看作是控制权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对政治体制的操纵是将经济优势转变为控制权的一种方式。但破坏政治体制的公平在其他方面也具有道德重要性,例如它会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legitimacy)产生影响。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对不平等的这种反驳,以及讨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影响力的不平等问题,或者是一个影响力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我所列举的这四种反驳清楚地表明,对经济不平等的某些反驳并非仅仅体现了嫉妒。它们还表明,这些反驳所要求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向下拉平。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不正当的控制形式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即便消除这些东西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福祉。公平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经济机会可能会导致穷人过得更好,但这不是人们想要建立公平制度的唯一理由。穷人有理由想要拥有平等的机会(即想要得到公平对待),即使这最终不会导致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机会平等意味着穷人在经济上变得更糟,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充分的 理由想要实现机会平等。)
平等的关切: 我刚列举的这些对不平等的反驳都是基于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但与此不同,还有一些对不平等的反驳是基于这种不平等的产生方式。例如,基于平等的关切(equal concern)的反驳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反驳适用于以下这种情况:某个机构或能动者(agent)应当把一些利益给予某一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但它只把这些利益给予其中的部分成员,或者给予部分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多的利益。
举例来说,假设市政当局有义务为所有居民提供铺设的道路和卫生设施。但如果市政当局在没有提供特殊证成的情况下,就向一些人提供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服务,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正当的。比如说,市政当局在富裕的街区比在贫穷的街区更频繁地重铺道路,或者在市长的朋友或某个宗教团体成员居住的地区更频繁地修整街道,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不正当的。但并不是每一次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为一些人提供某项服务而没有对其他人也如此,就都违背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例如,如果地质因素使得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难维护道路的通行,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道路维护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就不是不正当的,因为对这种做法的证成并不要求该地区居民的利益比其他地区居民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10] 我会在第二章讨论这一要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算作建立在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
公平的收入分配: 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中,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平均薪酬的20倍。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比例迅速增长,并在2000年达到了376∶1的高峰。2014年,这个比例仍然是303∶1,“高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的任何时期”。 [11] 此外,“从1978年到201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高管的薪酬增长了997%,几乎是股市增长的两倍,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员工年薪的缓慢增长,因为后者只增长了10.5%。” [12]
这种不平等看起来显然会引起反对。但它之所以引起反对,不是因为它表明了平等关切的失败。相关的利益并不是某个能动者有义务去提供但却不平等地提供的利益。相反,这些利益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参与经济而获得的利益。不过有人可能会反驳道,这些数字表明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缺失就可能使这种制度变得不公平。我已经提到了机会平等,并且我会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然而,目前的反驳有所不同。反对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是基于不平等的报酬被分配给某些经济职务或职位的方式,而不是人们缺少竞争这些职位的机会。由此便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公平会提出什么要求呢?我将在第九章讨论这个问题。
让我对上述的讨论稍做总结。我已经确定了六种理由,即六种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以及寻求消除或减少不平等的理由:
(1)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
(2)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
(3)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
(4)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
(5)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某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
(6)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因为它由不公平的经济制度所产生。
根据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的观点,无论(非自愿的)不平等发生在哪里,不平等都是坏的。 [13] 与运气平等主义不同,我所列举的这些对不平等的反驳都预设了不平等的相关人员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关系或互动。不正当的地位不平等预设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屈辱感或自尊受损成为合理的感受。因此,这种反驳就不适用于那些彼此之间没有互动的人。而基于控制的反驳仅仅适用于不平等涉及或导致某种形式的控制权。此外,基于缺乏平等关切的反驳则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或机构有义务去提供相关的利益。最后,基于干预经济机会和干预政治平等的反驳,以及基于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反驳也都预设了相关人员参与或服从某种制度,而公平的要求适用于这种制度。一旦我们将不平等与所有这些关系因素和制度因素分开,那么我们就不清楚不平等是否应当受到反对了。 [14]
在反对不平等的这些理由当中,有许多理由只适用于负有某些义务的制度,或只适用于与某些正义的要求相关的制度。这个事实可能会使读者把我的观点等同于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正义的政治概念”,即正义只适用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 [15] 但我的主张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这个概念不同。我所描述的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并非都以共享的制度为前提,并且在涉及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制度既不需要与某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范围,也不需要由某个国家来强制执行。例如,我在第八章中讨论的那种经济制度就不受国界的限制。
除了我所列举的这些理由,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理由来支持平等或反对不平等。但我将集中讨论我所列出的这些反驳,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因为它们建立在某些价值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价值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规范性问题。并非所有对不平等的反驳都会带来这样的问题。例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被反对,可能是因为它会损害健康。 [16] 有人也可能论证,更大程度的平等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不平等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或者因为平等会培养更强烈的团结意识和为共同利益努力的意愿,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如果这些主张背后的经验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把不平等视为一件坏事。然而,我不是在讨论这些理由,因为它们诉诸的价值对我而言并没有任何令人困惑的地方。例如,关于“不健康是不是坏的(bad)”,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好追问的。所以这些反驳是否适用纯粹是经验性的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会坚持主张,我们根本就不应当反对当下社会的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来自个人自由的合法运用,并且那些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的措施都是对这些自由的不正当干涉。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这种反驳,并考察这种反驳可能会依据的那些自由的观念。对经济不平等的另一种可能的证成是,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应得(deserve)更多的报酬。我会在第八章考察应得这个观念,并探究它是否可以作为对经济不平等的证成,或者是否可以作为对经济不平等的反驳。
在第九章中,我将审视某种关于不公平的观念,即我刚提及的最后一个反驳所依据的那种观念,并且我会探究这种基于不公平的反驳和我讨论过的其他反驳如何应用到近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加剧。第十章是对本书主要论题的总结。
[1] Justify的具体含义是证明某事物是正当的或合理的。依照国内目前的常见译法,本书同样把它译为“证成”。相应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倾向于把justified译为“得到证成的”和“获得证成的”等;但在少数情况下,为了保持译文的流畅,本书也会把它译成“有正当理由的”。——译者注
[2]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60-4.(本书的脚注将只引用著作的标题,完整的出版信息请见参考文献。)
[3] 在整本书中,当讨论人物且不涉及其性别时,作者都用“他或她”(he or she)这种表述方式来避免性别歧视。——译者注
[4] 参见Michael Marmot, Status Syndrome: How your Social Standing Directly Affects Your Healt,以及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对此的讨论,参见Martin O’Neill, “The Facts of Inequality”。
[5] 作者在本书中用“objectionable”来形容某个事物应当受到我们的反对,或者说它是我们有理由来反对的对象,因此本书倾向于把“objectionable”译为“应被反对的”和“引起反对的”等。同时为了保持译文的流畅,本书在部分情况下也会把它译成“不正当的”。——译者注
[6] 参见Derek Parfit, “Equality or Priority?”,以及Harry Frankfurt, “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和On Inequality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Martin O’ Neill, “What Should Egalitarians Believe”。法兰克福(Frankfurt)的中心论点是,我们应当关注“充足”(sufficiency)——每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关注平等——某些人的拥有物与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的差异(On Inequality ,7 et passim)。然而,他承认我们可能有好的“派生”理由去反对不平等,这些理由并不以平等的道德价值作为依据(On Inequality ,9,16—17)。他接着提到了许多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我将在本书的后面讨论这些理由。因此,我认为法兰克福只是在反对我所区分的狭义的平等主义理由。
[7]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ix.
[8]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351-2. 转引自Amartya Sen in Inequality Reexamined , 115。
[9] 马尔默(Marmot)等人认为,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看起来主要是通过我刚才所列举的这两种不平等的后果来实现的,即社会地位低下的体验和受他人控制的体验(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之中)。参见Michael Marmot et al., “Employment Grad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British Civil Servants”,以及我在脚注2中所引用的其他著作。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此提出了质疑,参见“What do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ell us about the Injustice of Health Inequalities?”, 270–2。
[10] 我把这称为“平等关切的要求”,而不是“平等对待的要求”(equal treatment)。因为它并不适用于那些被提供的利益,而是适用于这些利益能够获得证成的方式。
[11] 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 “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 2.
[12] Mishel and Davis, “Top CEOs,” 1-2.
[13] 例如,参见G. A. 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和Richard Arneson,“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这种观点是帕菲特(Parfit)在《平等还是优先?》(“Equality or Priority?”)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目的论的平等主义”(Telic Egalitarianism)的一个例子。“运气平等主义”这个术语是由这一观点的批评者——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在《平等的要点是什么?》(“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这篇文章中创造出来的。安德森支持的平等观与我的看法一样,都是一种关系性的观点(参见她的文章第313页及其他页码)。对此的批判性讨论,参见Samuel Scheffler, “What is Egalitarianism?”。
[14] 尤其是,G.A.科恩(G. A. Cohen)在《社会主义有何不可呢?》(Why Not Socialism? )这本书里对不平等的反驳,就极大地依赖于某种特殊的个人关系,即他的野营旅行例子所涉及的那种个人关系。
[15]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对这个概念的批判性讨论,参见Joshua Cohen and Charles Sabel,“Extra Rempublicam Nulla Justitia?”,以及A. J. Julius, “Nagel’s Atlas”。
[16] 参见脚注2中所引用的著作。
在第一章中,我将违反平等关切的行为列为一种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现象。我提及以下这些情况作为例子:市政府为市民提供了诸如铺路、卫生或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但它为一部分市民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却远远低于它为另一部分市民所提供的服务水平。而后者之所以受到青睐,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宗教观点,也可能因为他们是重要公职人员的朋友。
对不平等的这种反驳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有义务把一些福利提供给某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在此究竟预设了什么样的义务,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这种反驳就只适用于这种不平等,即不平等来自该能动者未能成功地向这个义务所针对的全部对象履行这个义务。
例如,考虑以下这些事实。在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4.2岁;在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则是70.4岁;但在马拉维,它只有37.1岁。这让人感到震惊,并且迫切需要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关于马拉维人的预期寿命的事实令人感到震惊,并亟须人们采取行动。人们经常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问题,有时候还把它称为“国际预期寿命差距”。然而,尽管这些事实非常令人不安,但我不认为在这个例子中,不平等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对象。
马拉维人的预期寿命如此之低是非常糟糕的。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要高得多,这一事实具有什么相关性呢?这种差异之所以是相关的,仅仅可能因为它表明人类不必这么早就死去。鉴于目前可资利用的技术,人类能够活得更久,并且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确实也活得更久。所以,马拉维男性的低预期寿命现象令人震惊的一个原因是,它是能够避免的。但把这种情况称为“国际预期寿命差距”意味着这三个国家的男性在预期寿命上的巨大差异 本身就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而它具有这种重要性对我而言则是不明确的。在我看来,重要的只是马拉维人的低预期寿命,而不是它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预期寿命上的差距。
相比之下,让我们来考虑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地区和种族上的差异。在美国预期寿命最长的前10%的县,77%的白人男性活到了70岁,而出生在这些县的黑人男性只有68%的人活到了这个年龄。在预期寿命最短的前10%的县,情况更糟糕。在这些县出生的白人男性,61%的人活到了70岁,而黑人男子只有45%。 [1]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3年的报告,美国白人每10万人中有1.2例肺结核病,而黑人每10万人中有10.2例肺结核病。白人婴儿死亡率为5.8‰,黑人则为13.7‰。 [2] 这些特征可能部分是由贫困造成的,但它们只要是由以下这个事实导致的,那么它们也提出了平等的问题,特别是平等关切的问题:公共机构在履行提供医疗护理和其他公共卫生条件的义务时,比起黑人和其他地区的人,这些机构向白人和某些地区的人更充分地提供了这些好处。一种更普遍的种族歧视态度在解释这种医疗差别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我所提及的其他例子中,不平等的对待方式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偏袒形式来得到解释一样。但即便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例子所共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切,它在道德上仍然应当遭到反对。
说国际预期寿命差异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不在于它所包含的不平等(或至少说,比起美国国内预期寿命的种族差异,这种不平等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遭到反对的),这并不是在说,这些国际差异不会引起正义的问题。比方说,如果马拉维人的低预期寿命是由贫困引起的,并且这种贫困是殖民国家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的,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不幸的情况(例如干旱或海啸所造成的结果),即便其他国家有人道主义的理由来帮忙缓解这种不幸。但根本的反驳仍然不是不平等的问题。如果我的钱之所以比你的钱更少,是因为黑客盗窃了我的银行账户,这当然是糟糕的,但糟糕的理由却不是基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如果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形成低预期寿命的这种贫困,不仅是过去殖民活动的产物,而且也由当前不正义的国际贸易体制所造成,那么在解释这些体制为什么不正义时,平等的观念或许能够发挥某种作用。但这并不是关于预期寿命的事实本身所暗示的平等问题。我的观点是,关于美国人在预期寿命上的种族差距,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平等问题,但国际预期寿命差异的例子似乎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它提出的是另一种严重的道德问题。
假设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因某种新疾病的出现而缩短了,从而减少了相关的不平等,但预期寿命的国际差异所引起的反对却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对国际预期寿命差异的反对不是基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因为假设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出于同样的原因也缩短了,但美国健康状况的种族差距所引起的反对同样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这种差距之所以引起反对,并不在于不平等这一纯粹的事实,而在于造成不平等的那种因素——对平等关切的违背。
我在第一章中描述并捍卫了一种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性见解(relational view),上述的讨论也阐明了这种见解的一个总体观点。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的例子中,它们引起反对的地方都不在于预期寿命不平等这一纯粹的事实。从根本上讲,考虑到现有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反对,是因为有些人的寿命比他们本来能够拥有的寿命要短得多。只有当不平等能够说明造成这些差异的制度或其他因素之所以会引起反对,不平等才是相关的。国际例子和国内例子的区别就在于,在国内的例子中,预期寿命的差异是由重要制度未能满足平等关切的要求造成的,而国际的例子则并非如此。 [3] 如果这种应该遭到反对的不平等减少了,那么对当前情况的一种 反对意见也将减轻,即便这会降低白人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并且也没有提高黑人的预期寿命。 [4] 这在总体上是否可被证成,则是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本章的目的是更详细地考察平等关切这一要求,特别是理解它所涉及的平等观。如果一个机构对其公民的义务只要求它以某种方式对待这些公民(例如不去侵犯他们诺齐克式的权利),那么即使这项义务平等地归于所有公民,平等的观念也难以解释当这项义务只为一些人而没有为其他人履行时所涉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构对待某些人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且无论它是否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它同样都是错误的。这些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相同的 权利)。但是平等的观念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侵犯这些权利是错误的。
一些人主张,平等的观念——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平等关切”的观念——是空洞的。因为那些看起来违反了这一要求的行为,它们的错误之处总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被解释为它们侵犯了一些根本的、非比较性的权利。 [5] 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平等在解释不平等关切的错误之处时,确实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考虑基础教育经费不平等的问题。美国每一个州的宪法都会要求该州为所有儿童提供基础教育。例如,新泽西州的宪法写道:“立法机关应规定:维护和支持一个全面有效的免费公立学校体系,用以指导该州所有5岁至18岁的儿童。” [6]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这一要求“必须被理解为包含了当代背景下所需要的教育机会,以便为儿童作为公民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手做好准备”。 [7] 如果州政府没有为某些儿童提供这种程度的教育,那么这会违反一项具体的、非比较性的要求。因为新泽西州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所以这导致了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面临一系列的案件。 [8] 但如果州政府向所有儿童都提供了这种程度的教育,尽管有些儿童还有机会接受由父母或私立学校所提供的额外教育,这种情况并不会违反这项 非比较性的要求。然而,如果州政府本身只为一部分儿童提供某种高于最低限度的教育,而没有为所有儿童提供类似的教育,那么这将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 [9] 这种比较性反驳的合理性看起来依赖于这个事实,即教育是一种竞争性的好处。如果一个州的一部分学生接受了更高程度的教育,那么这将使其他人“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手”而处于劣势。但我认为针对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比较性反驳并不依赖于这种竞争因素。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另一个例子,即对防止错误定罪的程序保护。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是不正义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它未能充分地提供这种保护。美国的法律制度在这种非比较性的意义上是不正义的,因为贫穷的被告人(尤其是黑人)缺乏足够的保护来避免被错误地定罪。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法律辩护,而且经常被迫接受他们本不应该接受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s)。
任何一套程序保护都是不完美的,并且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我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不完美的)保护,它使得一个为每个人都提供这种保护的法律体系不会受到这种非比较性的程序不正义的指责。但是,如果这种制度为一些公民提供了比其他公民更高程度的程序保护(例如,如果对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宗教成员的刑事指控必须有更高标准的证据作为支持),那么在缺乏某些特殊证成的情况下,这在比较性的 意义上就是不正义的。即使这种法律制度不会侵犯非比较性的权利,但它也没有提供“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前面提到的例子,即医疗、铺路或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供应。也许政府具有一种(非比较性的)义务为所有人提供这些服务,以便保障所有人在这些服务上都能达到某种最低水平。但不管政府是否具有这种义务,只要政府在缺乏特殊证成的情况下,向不同的群体提供了不平等的服务水平,那么这便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对待方式上的差异可由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背景来加以解释,而这些偏见和歧视本身在道德上就是不正当的。但是,基于那些非比较性的或比较性的理由,不充分的或不平等的供应水平就会是错误的,并且那些理由独立于这种不正当的背景条件。因此,这些情况可能涉及三种类型的错误:一是没有充分提供某些福利的非比较性错误,二是不平等关切的比较性错误,三是种族歧视的错误。
这些不同的错误有时候会难以分解。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种族脸谱化(racial profiling)的情况。例如,在警察拦截和搜查汽车的实践活动中,他们需要依据司机的潜在犯罪证据来证成这些拦截和搜查的行为,但是他们针对黑人司机所需要的证据却少于针对白人司机所需要的证据。这显然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但它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如果政策要求警察需要获得某种程度的证据才能证明拦截白人司机是正当的,而且这种程度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最低限度的保护,使得人们免受这种拦截的干扰,并且这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的保护。那么,允许警察依据较少的潜在犯罪证据去拦截黑人司机,这种做法就既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也是一种不平等对待的不正当形式。某种关于种族歧视的一般背景或许可以解释这些比较性的和非比较性的错误,但这些错误是某些更一般形式的错误,并且也独立于种族歧视这一特定的原因。
当政府为某些人投入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以便提供某种特定的福利时,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表明政府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如果地质因素导致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难维护道路的通行,那么政府在这些地区的道路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出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居民和城里其他地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切。同样,如果市政当局在特殊教育的班级比在非残疾学生的班级投入更多的资金,这也没有违反平等的关切,因为这并不表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利益比其他儿童的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就我迄今所考虑的情况而言,例如公共卫生、铺路、教育和对错误定罪的保护等,我都假定了政府有特定的义务来提供这些福利,至少有义务使人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一定的福利水平。而只要这些供应的成本不是特别高,那么这种假定看起来就是合理的。但即便一些机构没有义务去提供某种特定的好处,只要这些机构负有一般性的义务去为某个群体提供福利,那么平等关切的要求也能够适用于这些机构。有一些福利是政府可以选择是否要提供的,例如公共游泳池、溜冰场和高尔夫球场或许就属于这种福利。然而,一旦政府提供了这种福利,那么它就不能只让一部分公民可以合法地获得这种福利。而且我想说,如果政府提供这些设施的方式会导致只有某些社区的居民才有机会使用这些设施,那么它可能也会遭到反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平等地使所有公民受益。我们可能需要某些政府设施,例如行政大楼或军事机构。这些设施通过服务于一般的公共目的,从而为所有人都提供了福利。但除此之外,它们还可以为其所在地的居民提供额外的福利,例如增加就业机会。这本身并不违反我所描述的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相关的设施为一些人所带来的这些福利并不是建设它们的理由(这与我提到的诸如娱乐设施等其他情况恰好相反)。对建设这些设施的证成反而依据的是它们给所有人都带来的那些福利。军事设施和其他公共建筑必须建立在某个地方,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些福利。一些公民获得了这些福利,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违反平等的关切。但是,如果公共设施始终在某一个地区建造,并且缺乏任何其他的证成,那么这看起来就反映了政策更偏袒该地区公民的利益,而非其他公民的类似利益。因此,这项政策便违反了我正在讨论的平等关切的要求。
为什么福利的比较水平会以这种方式引起重视?如果相关的好处是竞争性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平等的相关性,因为提供更高水平的好处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占有优势。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是一种竞争性的好处,但诸如铺路和照明之类的公共服务则不是。比起不健康的人而言,更健康的人确实具有一种竞争优势,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便可以作为机会平等的组成部分而获得证成。 [10] 但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对医疗服务的不平等供应的唯一反驳。问题在于,在涉及非竞争性好处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应当反对不平等的供应呢?
事实上,平等对待 (treatment)的要求看起来容易遭到某种版本的向下拉平反驳。正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说:“平等主义的原则常常导致浪费。” [11] 拉兹说,如果我们无法把某种好处平等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可用来分配,那么平等主义的原则会要求我们不把它提供给任何一个人。
这一反驳的合理性来自拉兹对平等主义原则的特殊理解方式。拉兹把平等主义原则的典范形式理解为:“如果有些F拥有G,那么所有没拥有G的F就都有获得G的权利。” [12] 这个表述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我所理解的平等关切的要求。首先,拉兹所说的平等主义原则简单地适用于人们所拥有 的好处,而不管这些好处是怎么产生的。相比之下,我所捍卫的平等关切的要求只适用于单个能动者对好处的供应 。其次,正如我所说的,平等关切并不总是要求能动者向个人提供同等数量的好处。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某些福利的不平等供应才会违反平等的关切:如果所有受影响的人的利益都获得恰当的重视,那么这种不平等的供应将无法得到证成。换言之,在以下这些情况,不平等就不一定与平等的关切不相容: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来平等地让每个人受益;或者,为一些人提供与其他人同等水平的福利,这种做法在其他方面是无法实现的或困难重重的,甚至(像我所说的那样)会带来特别高的代价。虽然在一些例子中,拉兹关于“浪费的指责”看起来具有初步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平等关切的要求所具有的这种灵活性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例子。
通过考虑另一种不同的反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当某种不平等得到“好的理由”的支持时,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便与平等关切的要求相容。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我所捍卫的平等关切只是一种有限度的 (pro tanto)要求,并且在我描述的那些情况下,这种要求被压倒(overridden)了。就某些好处而言,例如对错误定罪的保护,这看起来特别令人不安。作为回应,我需要多谈一谈在应用平等关切的要求时所涉及的利益权衡问题。
在我讨论的那些情况下,道德所要求的那种关切具有两方面内容:一个是非比较性的,另一个是比较性的。一项政策可能缺乏对某些人的关切,而这种关切的缺失之所以是不正当的,可能基于以下两种理由:第一,与其他价值相比,证成这项政策的方式没有充分地 重视这些人的利益;第二,这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少的 重视。我们可以用对错误定罪的程序保护为例来说明这两种反驳。一个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它没有为被告人提供道德所要求的那种保护而遭到反对。也就是说,比起提供这些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它没有充分重视被告人免受错误定罪的利益。不过正如我所说的,即便一个法律制度对所有人都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但只要它对一些人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并且这表明它更重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那么它也会遭到反对。
因此,一些考虑因素便可以通过上述这两种途径来为某些对待方式提供“好的理由”,否则这些对待方式就会遭到反对。这些考虑因素有可能提供足够好的理由来支持为一些人提供某种低于最低水平的好处,因为这些理由比那些支持提供最低水平的好处的理由更重要。当然,哪些考虑因素才算是支持这种做法的好理由,这显然会因相关好处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某些考虑因素会比人们从一种适当水平的道路翻新中所获得的利益更重要,但要比人们从避免错误定罪的保护中所获得的利益更重要则无疑会困难得多。这里的要点仅仅是,如果我们具有这种好的理由,那么即便我们没有以通常要求的最低水平来提供某种好处,这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充分重视人们从拥有这种好处中所获得的利益。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考虑因素如何能够成为好的理由以便支持向一些人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好处(当两者都高于最低水平时),以及这需要满足哪些要求。虽然某项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某种好处的不平等供应,但支持这项政策的理由却可能与这种好处给受其影响的人带来的福利无关。例如,一个地区可能需要更高质量的道路,以便为该地区工业厂房服务的卡车能够使用这些道路。一些居民也可能因为附近的科研机构需要架线而获得了更好的宽带通讯。当应用这些理由去提供更好的服务时,这种做法并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对这种做法的证成没有涉及某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这里的要点在于,当某些考虑因素以这种方式来证成对好处的不平等供应时,它们的证成方式并不包含压倒平等关切本身的要求。恰恰相反,这些考虑因素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方式表明,即使福利的供应不尽相同,这些个人利益也都得到了平等的考虑。
把权衡互相竞争的考虑因素纳入平等关切本身的范围之内,这似乎走得太远了。 [13] 例如,假设一项亟须的军事拨款法案包含了这项规定:它要求把它将购入的所有设施都放置在该国的某一个地区。这项规定有利于该地区居民的利益,但它缺乏任何证成,所以这项法案看起来违反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但受益地区的立法者坚持执行这一规定,否则他们将阻碍法案的通过。再假设,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利益,这项法案的通过(而非不通过)经综合权衡之后会获得证成,那么基于我所提议的推理方式,这项法案的通过似乎最终仍然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这个明显的悖论可以通过这个区分来加以解释,即区分法案本身是否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以及在特定的条件下,该法案的通过 是否符合这一要求。我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是”。
这个例子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来防止误解,因为我给这个要求所起的名称可能在某个方面会误导别人。“平等的关切 ”可能暗示,它要求某些能动者具有某种(关切的)态度。但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行动或一项政策是否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取决于支持它的理由:当以正确的方式来考虑所有受影响人员的利益时,它是否可被证成。而在我们刚才所考虑的情况之中,无论我们是将这个要求应用于一项政策,还是应用于在某些情况下制定这项政策的决定,这一点都同样为真。这个要求关注的是支持这一决定的理由,而不是决策者的态度。
确定一项政策是否与平等关切的要求相容,这涉及权衡人们拥有相关好处所带来的利益和其他相互竞争的考虑因素。而这一事实似乎有可能使这一要求沦为一项非比较性的要求,即每个人的利益——如他的诺齐克式权利——应受到应有的(due)重视。但情况并非如此。正如我所解释的,平等关切的要求依然保留了它的比较性特征。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的利益应当受到某些能动者的适当 重视,这不仅要求这些利益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还要求这些利益应当受到与(某些)其他人的利益相同的 重视。
这就提出了这项平等关切的要求何时适用的问题。我说过,它适用于有义务为某些人提供福利的能动者。但是什么样的能动者负有这种义务呢,以及他们对谁负有这种义务呢?我对这个问题缺乏一般性的答案。幸运的是,对于我当前的有限目的而言,我不认为这样的答案是必需的。我在这本书的目的是确定对不平等的各种反驳,以及确定这些反驳所依据的平等观(如果有的话)。本章的目的是审视这样一个具体的反驳,即反驳因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而引起的不平等。因此,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提供理由使人们相信存在着这种义务,这就足够了,而这种义务确实也解释了我们对于不平等持有一类独特的反驳。
在我看来,我所列举的这些例子使得以下这两点看起来非常合理:第一,地方政府和各国政府对其公民负有这种义务;第二,平等关切的要求由这种义务而产生。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当下,德国西部的学校比东部的学校拥有更多的经费,那么这至少会引起基于不平等关切的初步反驳。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时候,这种反驳就会变得不合理。
通过概述政府为什么应当遵守这项要求,我们可以对上述这个诉诸案例的论证提供一些支持。如果政府所行使的权力——制定和执行法律以及要求公民纳税的权力——依赖于他们为公民所提供的福利,那么这些福利就必须提供给所有 公民(所有被要求守法和纳税的人)。否则其他人就没有理由接受政府权力的这种证成方式。此外,在证成政府的政策时,为什么有些公民应该接受其他人的利益比他们的利益更重要呢?尤其是他们还被要求应当通过纳税和遵守其他法律来一起支持这些政策。
如果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是合理的,即政府对其公民应当遵守平等关切的要求,那么这就足以确立我在本章中的主要观点。不过,我怀疑这种义务并不局限于政府,父母对其子女也负有这种平等关切的义务。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平等关切的要求能够普遍地适用到个体身上,即便个体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如果我捐出一大笔资金来帮助某个国家的穷人,那么我可能会受到这种优先主义的反驳:我本来应当帮助其他地区的人,因为他们更需要得到帮助。但我认为,我不会因为我只向一些人提供了援助,而没有向其他有同等需求的人也提供援助,从而遭到一种基于不平等关切的指责。
私人机构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可能负有这种义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举例来说,即便某个慈善机构的设立只是为了帮助某些大学,它也不会因为它没有对其他大学的需求给予同等的重视而遭到反对。同样,即使某个基金会的成立只是为了研究和治疗某一种疾病,它也不会因为它没有关注那些患有其他疾病的人而遭到反对。但是,如果它已经征集捐款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免税的地位,同时它又只为某一地区的居民提供帮助,而忽视其他地区那些患有相同疾病的人,那么它可能会遭到反对。然而,这一反驳似乎与适用于政府的平等关切要求有所不同,因为它看起来是基于捐助者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对受益人所负有的义务。 [14] 一个更好的例子可能是工会,因为正是工会的成员建立并支持着工会。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第一,工会必须遵守这一要求,即它的决策和政策应当可被证成地把所有成员的利益都纳入考虑之中,并平等地重视这些利益;第二,这项平等关切的要求是工会对其成员所负有的义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成员既是受益人,也是贡献者。
每当平等关切这一义务所适用的对象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平等的考虑时,这个不偏不倚的要求通常会伴随着对偏袒 (partiality)的允许。由于某些人并非平等关切的适用对象,所以偏袒会使得这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便引出了这个问题:这种偏袒是否与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基本的道德平等”这一观念相容?在此,基本的道德平等指的是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很重要。我相信这些观念事实上是相容的。尽管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但没有任何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会规定我们作为个体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都要平等地重视每个人的利益。这种规定会带来难以置信的约束,它甚至不可能实现。
声称各国政府对于境外人员的利益也负有这种关切的义务可能会更合理。而另一个更强硬的主张则是,我们作为个体确实负有这种义务,并且对政府的一种证成形式就在于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履行这一义务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比个体的行动更有效,而且不同于我已经提过的那种针对个体的普遍义务,这种方式不会具有侵扰性。
即便对于某些好处的供应,例如提供健康所需的条件和体面生活所需的经济商品,政府负有上述这种平等关切的义务,但对于另外一些好处的供应,政府还会对其公民负有其他特殊的平等关切的义务。这些另外的好处包括需要由当地提供并受当地决策所支配的好处,例如铺路和教育,而且通常还包括政府有责任通过民主程序来提供的那些更进一步的好处。
如果各国政府负有一种更广泛的义务向境外人员提供某些好处,那么这一特定的义务所适用的对象便能够提出平等关切的要求。但各国政府是否负有这种义务,将取决于这种义务的缺失会带来道德上难以承受的后果这一事实是否构成了对这种义务的证成。如果这一事实确实构成了对这种义务的证成,那么这个主张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另一个相关的主张,即这种义务是防止这些后果的有效途径。而这个相关的主张又将取决于外来者能够有效地提供哪些好处。
这使我回想起我一开始对国际预期寿命差距和国内预期寿命差距所做的对比。我们可以论证,预期寿命的国际差异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不平等对待的问题。或许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是任何现有的单一机构没有平等地重视不同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对其他健康条件的需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需要建立某个有义务为所有人提供这些好处的机构。
通过下述这两个步骤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结论。第一步是这个(非比较性的)主张:为了让许多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个负有普遍义务的机构是必需的(并且这是确保这些利益得到满足的有效途径)。第二步则主张,目前存在的这种国际差距违反了平等对待的要求,而这个机构应当遵守这个要求。但是,即便这个论证是正确的,我认为情况依然如此: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对国际预期寿命差距的反对,针对的并不是它所涉及的不平等。
[1] Mark R. Cullen, Clint Cummins, and Victor R. Fuchs, “Geographic and Racial Variation in Premature Mortality in the U.S.: Analyzing the Disparities.”引用的数字来自1999—2001年的死亡率。
[2] CDC, Health Disparities and Inequalities Report-United States, 2013.
[3] 平等关切的要求可被理解为意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例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把它理解为这种要求,即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必须以平等对待每个公民的方式来获得证成。(参见Sovereign Virtue, 6。)我会接受这一要求,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且在此框架之内,我要讨论的那些对不平等的反驳全都可以被理解。但我将用“平等的关切”这一术语来确定违反这项规定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即没有平等地履行某项义务,从而导致某些利益的不平等供应。并非所有我要讨论的对不平等的反驳都依赖于这种义务。总体而言,那种被德沃金视为起点的平等关切的观念,会通过以下这两种方式来反对不平等的结果:当我们关注政府负有义务去提供利益时(正如本章所谈论的),它以一种方式提出了反驳;而当我们关注证成一个经济合作体制时(正如第九章所讨论的),它则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反驳。
[4] 我感谢詹姆斯·布兰特(James Brandt)在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
[5] 参见Peter Westen, “The Empty Idea of Equality”。尽管韦斯顿(Westen)的文章标题提到了“平等”,但作为宪法律师,他在写作此文时主要关注的是“平等对待”这个特殊的观念,也就是我所说的“平等关切”。对于比较性的错误和非比较性的错误这个问题的更一般性的讨论,参见Joel Feinberg, “Non-Comparative Justice”。
[6] New Jersey Constitution, Article VIII, Section IV.
[7] Robinson v. Cahill 62 N.J. at 515.
[8] 关于新泽西州的这个争论,对此的概述可参见“School Funding Cases in New Jersey,” <http://schoolfundinginfo/2015/01/school-funding-cases-in-new-jersey>。关于堪萨斯州的类似争论,参见“School Finding Cases in Kansas,” <http:// schoolfunding.info/2015/01/school-funding-cases-in-kansas-2>。
[9] 一个允许更富裕的学区提供更高教育水平的教育经费制度,是否违反了平等关切的要求,这将取决于以下这个问题:这个经费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视为州政府的一个政策,并且州政府通过这个政策来履行提供教育的义务;或者与此相反,提供更好教育的市政当局是否被视为独立的能动者,例如被视为家长的私人团体。
[10] 正如诺曼·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对此所提出的论证。参见他的Just Health Care 。
[11]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 227.
[12] Raz, Morality of Freedom , 225.
[13] 我感谢杰德·卢因森(Jed Lewinsohn)提出这个可能的反驳。
[14] 我感谢安德鲁·戈尔德(Andrew Gold)指出了这一点。
种姓制度以及带有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社会都是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我们可能有若干理由来反对这类社会。在这一章中,我关注的是这种反驳:它建立在这类社会所包含的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我的目的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反驳,并考虑我们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以类似的理由来反对经济不平等。我也将考虑,一个彻底任人唯才的(meritocratic)社会是否会受到这类反驳。
在有种姓和等级差别的社会中,以及在带有种族歧视的社会里,有些人会仅仅因为他们的出生背景就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就业形式。他们还经常被剥夺基本的政治权利,例如选举权和参政权,而且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他们往往也无法获得某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本应提供给所有人。此外,当我所说的“团体性的好处” (associational goods)涉及其他群体的成员时,他们还会被视为没资格得到这些好处。例如,其他群体的人会认为他们不太适合成为同事、潜在的朋友、可能的婚姻伴侣,甚至邻居。
当人们以这些方式遭受歧视时,这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重要的机会,并且这种做法缺乏任何好的理由作为依据。即便这是由纯粹的任意行为造成的,或者在公共服务的例子中,这是由政府官员对政治盟友的偏袒造成的,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但在我所关注的那种歧视的意义上,那些遭受歧视的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这些好处,是基于这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关于他们的某些事实——例如他们的种族、性别或宗教——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没资格获得这些好处。按照我对歧视的理解,人们受到这种普遍流行的低人一等的观点的影响,即认为他们对于重要的好处和机会只具有较少的资格以及他们不太适合参与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这个事实是歧视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歧视的错误之处依赖于这个事实:它依据的那些诸如种族和性别之类的特征并不能证成它所包含的态度和差别对待。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歧视者往往会诉诸某些经验概括,它们看起来提供了更好的证成,比如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是不可靠的或太懒惰了,或者他们不具备那些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然而,这些概括通常都是错误的。但是,即使它们是正确的,它们也不能证成歧视所包含的那种对待方式。以不可靠为由拒绝信任某人或拒绝让他承担责任,这需要证据来表明他这个人确实不可靠;而以缺乏相关能力为由拒绝给某人提供职位,则需要证据来表明他确实缺乏能力。关于某个人所属群体的统计事实并非总是具有相关的证成力量。 [1]
如果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开始把歧视性的对待方式和歧视所表达出来的态度视为具有正当的理由,那么这种歧视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这将对他们的“自尊”(self-respect)或“自重”(self-esteem)造成某种打击。这里的“自尊”或“自重”是在罗尔斯所说的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价值的感受,他的这种坚定的信念——他的善观念(他的人生计划)是值得执行的”和“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对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所具有的信心”。 [2]
但对于我正在考虑的这个反驳而言,某种低人一等的感受或丧失自尊的感受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人持有这些高人一等和低人一等的观点,并且导致我所描述的那种排挤和偏袒的实践活动稳固地存在,那么这个反驳就适用。当然,受到歧视的人也可能会认可与他们的地位相对应的那些职务和相关的价值,并在完成这些职务时错误地找到了(罗尔斯意义上的)自尊。这样他们就不会体验到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屈辱,但基于我现在正在关注的这些理由,相关的歧视仍然是不正当的。
无论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是将这种体验视为对他们的自尊或自重的打击,还是在完成分配给他们的职务时找到自尊和自重,那些没有以这种方式受到歧视的群体,他们的很多成员则很可能会将他们不具备这一群体特征视为关于他们自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并且也是他们的自尊的一个保障。而这一点也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理由,使得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以及他们的计划是值得追求的。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双方的态度都可能存在着某种病态:基于不恰当的理由而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命和活动,以及基于这些错误的理由来调节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3]
消除歧视或其他形式的地位不平等并不会导致应被反对的“向下拉平”——它没有让任何人受益并且使得某些人过得更糟。这也许会剥夺一些人的优越感,而且这些优越感可能是他们很重视的对象。但对于这种优越感的丧失,他们并不能(合理地)提出抱怨。所以在道德相关的意义上,这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糟,而且还会让那些受到歧视的人受益。 [4] 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以下这两种遭遇:一是在缺乏任何好理由的情况下就被剥夺了我所说的那些好处,二是受到我所描述的那种低人一等的态度的影响。他们的反驳并非仅仅是对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的嫉妒。
因此,我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实践面临着这三种反驳。第一,在缺乏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它禁止很多人去获取重要的好处和机会。第二,它剥夺了歧视者和被歧视者一种重要的好处,即人们彼此之间平等相待所具有的好处。第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导致很多人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对于那些属于“高人一等”的群体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价值观错误地建立在这种优越的地位之上。而那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一旦接受了这个判断,那么他们就会不恰当地轻视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如果那些遭受歧视的人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并且把他们的价值观建立在完成某些职务的基础之上——那些被指定为“唯一适合他们的职务”,那么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他们无疑是把这种积极的评价建立在错误的理由之上。
这些反驳在不同的程度上属于平等主义的反驳。第二个反驳是最明显的平等主义反驳,因为它建立在彼此平等相处这种价值之上。第一个反驳是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一些人被不正义地剥夺了重要的机会。但这种反驳可能是平等主义的反驳,也可能不是平等主义的反驳。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没有提供这些好处可能是一种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从而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它也可能体现了不平等的关切,从而是一种比较性的错误。第三个反驳所指出的问题是,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去评价自己和他人。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这是一种关于“善”(good)的错误,而不是一种关于“正当”(right)的错误。如果只有当人们犯下这种评价性的错误时,才会出现第一个反驳所关注的那种不正义,那么这就是一种“正当”对“善”(关于“善”的流行观点)的依赖。正如G. A. 科恩兴许会这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社会的风尚(ethos)。 [5]
现在我开始转向这个问题,即经济不平等如何会导致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这正如亚当·斯密所观察的,他说如果经济状况导致一些人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感到羞耻,那么这便构成了对这种经济状况的反驳。 [6] 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经济不平等如何会产生这种不正当的影响。
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机制是这样的:人们的穿着方式、生活方式和他们拥有或消费的东西——比如他们开什么样的车,或者他们是否有车,以及他们是否有电脑——可能标志着他们适合或不适合担任某些职务,尤其是更适合还是更不适合得到我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性的好处。由于他们能否获得这些东西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金钱数量,所以经济不平等会对穷人的地位产生这种影响。
慈继伟清楚地描述了这些影响。 [7] 他区分了他所说的三种“贫困的风险”,我认为他借助这个短语所指的是,通过这三种方式,贫困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坏事。如果缺钱威胁到一个人用来满足身体生存需求的能力,那么就会出现“生存贫困”。而当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重,但某个人却因为缺钱而无法按照这种方式生活时,这便导致了“地位贫困”。最后,如果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function),他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但某个人由于缺钱而无法实现这一点,那么他便处于“能动性贫困”(agency poverty)之中。举例来说,要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这包括拥有一份工作,或者做其他社会所要求的事情,以便能够获得一个人有理由想要的那些东西。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避免能动性贫困可能还包括拥有信用卡、住所和电话,或许还有上网。按照罗尔斯对“自尊”一词所下的定义——“对自己的人生计划的价值所具有的安全感以及执行这种计划的能力”,贫困的这三个方面都会对穷人的这种自尊造成威胁。
正如慈继伟所指出的,贫困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坏事的这三种理由,既密切相关又互相分离。一个自愿选择忍受生存贫困的苦行僧,可能不会在能动性或地位上有所损失。苦行僧可能还会受到钦佩,并且被视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慈继伟说,在某些时代,生存贫困并不意味着地位的缺失,而是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建设中是特别坚定的参与者,反而富裕可能带来猜疑和羞辱。相比之下,在今天的一些国家,拥有汽车是一个重要的地位象征,而一个人若像农民一样地生活则意味着他得不到尊重。 [8] 同样地,即使一个人充分地感受到自己作为能动者在发挥作用,例如拥有工作、以消费者的身份去参与经济活动、为人父母等,他也可能正在经历着地位贫困。
让我们在美国的背景中来说明这一点:在最近的一篇网络社论中,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回应了对穷人的批评,起因是穷人被指责在苹果手机等奢侈品上“浪费金钱”。 [9] 这位女士描述了在她的邻居被福利金办公室拒之门外之后,她的母亲如何以显眼的“名牌”服装打扮以及“名牌”手提包去福利金办公室帮邻居的孙女恢复了福利金的申领。她写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打扮得像样的问题(即干净而没有异味,不穿破烂的衣服),而是得看起来像某个人 ——像一个需要受到尊重的人。我认为作者在此的观点是,对于穷人(尤其是黑人)而言,拥有某种奢侈品是他们避免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 能动性贫困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是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良好作用的重要方式。
虽然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坏事,但它们之所以是坏事,却基于不同的理由。能动性贫困与这个事实有关,即缺钱会使一个人无法去做那些对特定的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些后果依赖于相关社会的组织方式。并且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有多种理由希望能够去做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正是这些理由使得能动性贫困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件坏事。贫困能够使得人们无法去做这些事情,这一点并不需要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所持有的歧视态度。但另一方面,地位贫困则依赖于这种态度。被其他人看作低人一等,并且被视为不适合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件坏事。然而,正如我刚才的例子所表明的,以这种方式被视为低人一等,也可能会妨碍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有效地发挥作用。贫穷可能通过 将一个人标记为“地位低下的人”而干扰了他的能动性。但贫穷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来干扰能动性,而地位低下则可能基于其他理由而应当受到反对。
我认为,这些观点把握到了亚当·斯密在我引述的那种段话中所思考的内容。斯密所说的那种由贫穷引起的感受包含了坚信别人认为自己(甚至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没资格,或者不如别人有资格去担任那些有价值的职务以及获得各种各样的团体性好处。它可能还包含了无法在社会中作为“正常的能动者”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造成一种人生失败的感觉。
我在前面讨论歧视和种姓制度时说过,这些制度所造成的伤害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去消除这些特权地位。如果经济不平等也造成了类似的伤害,那么这便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有限度的 (pro tanto)理由去优先支持一个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境况,即便这会降低一些人或者所有人的经济福利水平。然而,正如慈继伟所指出的,只有当某些态度普遍流行时,经济不平等才会带来地位贫困的伤害。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伤害也为改变这些态度提供了直接的理由。即使经济利益的分配保持不变,假设人们渴望财富和收入(至少超过某一个数字)的原因之一是想要获得优越感,那么这种态度的改变无疑会使富人失去某些东西。但是,他们却无法提出任何主张来反对这种损失。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嫉妒指责”的一种镜像(mirror image)。嫉妒指责是一种对要求减少不平等的反驳,它主张这些要求仅仅表达了某些无法被证成的欲望,即渴望其他人不会比你拥有更多的东西。与此相反,我刚才所描述的则是一种对抗拒 减少不平等的反驳,它主张这种抗拒仅仅表达了某些无法被证成的欲望,即渴望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正当与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社会态度在经济不平等和地位伤害之间起到了调解的作用,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这些态度包含了一些广泛流行的评价错误。人们认为收入和消费形式的差异具有某种重要性,但这些差异实际上并不具有这种重要性。如果可能的话,要避免我所提及的地位伤害,其中一种方法就在于纠正这些错误。
虽然我怀疑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纠正这些错误,但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在某个社会中,至少有一些错误得到了纠正。在托马斯·内格尔那篇讨论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文章里,他在末尾处写道:“当种族和性别的不正义已经减少了,我们仍将面临聪明人和笨蛋之间的严重不正义。因为他们都做出了类似的努力,但却得到如此不同的回报。” [10] 内格尔提到了经济奖励上的差异,但他所说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尊重上的差异,而后者正是我想要关注的对象。
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个社会中,除了才能之外,我们不会基于种族、性别或其他天生的偶然特征来对别人进行区别对待。我假定,社会上会有一些每个人都认为值得向往的职务和职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回报非常微薄,甚至根本就没有)。相反,这些职位之所以被认为值得向往,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些机会,而这些机会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来运用娴熟的才能。也许还因为这些职位构成了一种认可(recognition),它意味着那些有资格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在各个重要的方面都比其他人更成功地发展和运用某些能力,而这些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理由去重视并希望能够拥有的。我假定,人们纯粹依据优点来为这些职位选拔担任者,这里不存在歧视和偏袒,并且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职位的担任者都应得 这些职位,而且大家也都相信这一点是真的。至少在制度性的“应得”意义上,即某些得到证成的制度把这些职位和报酬分配给了这些担任者,这一点是真的。而只要这些职位构成了对某些优秀特征的恰当认可,那么我们还可以说,这些担任者在一种更深层次的、非制度性的意义上也应得这些职位:因为他们具有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身就使得这种认可形式成为一种恰当的形式。 [11]
我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它所认可的这种差异是否涉及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地位伤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一个彻底任人唯才的社会看起来就具有种姓社会的一些缺陷。 [12] 当然,比起这个社会,种姓社会更缺乏某些流动性。毕竟在这个社会里,任何阶层的儿童,只要他拥有才能,那么他都有可能“晋升”到更值得向往的职位。我已经假定,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拥有能胜任这些职位的才能是一件好事,而缺乏这些才能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比方说,所有父母都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才能。但是,为什么这些态度不等同于一种应被反对的地位等级呢?
按照我的假定,这些态度不包含任何事实错误。然而,即使它们不包含错误,或者说尤其是 它们不包含错误,那些缺乏这些才能的人不会感到自己没地位吗?并且这种地位的缺失还被证明是正当的。如何能够避免这一点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我们认可某些才能非常值得培养,它们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理由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去努力培养的才能,并且如果社会职务和职位允许人们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而运用这些才能,那么这些职务和职位就能够很好地获得证成;但与此同时,在这个社会中不会有人感到自己没地位和缺乏自尊——这种地位和自尊的缺失既得到了证成,又应当遭到反对。卢梭通过拒绝第一个前提来回应这个两难困境。他认为,人们之所以重视某些特殊的成就,只是把它们当作感受自己高人一等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这些成就的话,那么这不会导致任何损失。(他认为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而,与卢梭不同,我认为这种评价态度能够获得证成。某些形式的成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人们为达到这些成就而喜悦,以及为达不到它们而遗憾,这些都是恰当的感受。因此,我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避免我所描述的那些应被反对的后果呢,或者我们是否必须简单地把它们接受为生活的事实?
我之前说过,在我设想的社会中,所有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发展出某些能力,这些能力使他们有资格胜任一些特殊的位置,比如说考上最好的大学。而如果他们的孩子缺乏这些能力,家长就会感到失望。然而,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 某些能力和成就在社会中得到重视,而且还包括它们以何种方式 得到重视——这种重视对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 [13] 我已经假定,在我设想的社会中,人们重视那些让人有资格在高等教育中表现优异的能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发展这种能力,而且如果他们的孩子没这样做,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机会平等时所看到的,如果儿童要获得他们有理由想要的那种机会,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他们的成长环境要让他们认识到,发展这些能力是他们有理由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
然而,人们认为某些能力值得拥有,这是一回事;但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这些能力,或者如果他的孩子没资格考上最好的大学,那他的生活就被击垮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它是一种评价错误。即使人们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胜任理想职位的才能,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还有其他事情值得去做,即还有其他值得度过并且让人感到满足的生活。不理解这一点便犯了另一种类型的评价错误。由于某些环境能够引导人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生活具有多样性,因此对于每个人在理想上都应当拥有的那种机会而言,这些环境便构成了这种机会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14] 当我们认为一个完全任人唯才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应被反对的等级制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犯这种错误的社会,并且他们过度地关注某些特定形式的优点。
我们也可能把这个社会想象成这样:拥有这种优点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没有这种优点的人则感到低人一等,并且被别人“瞧不起”。这是另一种评价错误。一个人重视某些能力和成就,并为拥有这些能力和成就而感到高兴,这不一定意味着他相信这使得他高人一等,或者比其他人更重要。然而,虽然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可能很清楚,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很难将这些态度分开,并且这种实践的困难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希望社会各阶层的儿童都认识到在校表现优异和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两者所具有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儿童又不应该觉得自己比那些在这方面表现优异的人更低劣,也不应该认为这些表现优异的人会瞧不起他们(不管这些人的实际态度如何)。内格尔所说的“聪明人和笨蛋”暗含了这种类型的优越性和低劣性,当然这未必是他的意图所在。基于很多可理解的原因,这些高人一等和低人一等的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广泛流行,由此导致的自卑感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从而产生有害的政治后果。
要把对这些能力和成就的价值的认可与优越感和自卑感分离开来,这会因这些能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而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某些人重视的事物与我们相一致,并且他们拥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去追求那些事物,那么我们更喜欢与这些人交往,这并非不合情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罗尔斯关于“非比较性的群体”(noncomparing groups)的观点看作是认识到这一困难并试图减轻其影响的一种方式。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一个社会通过设立优势职位来奖励某些能力,这既需要通过“差别原则”的许可,也需要确保人们具有公平的机会平等来竞选这些职位。但罗尔斯说,即便社会奖励了这些能力,这些奖励上的差异也不一定会导致自尊的丧失。他认为情况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倾向于形成多个“非比较性的群体”,而在这些群体之中,人们主要与兴趣和能力相似的人交往。罗尔斯说,为了保护人们免于丧失自尊(即对他们的人生计划的价值失去信心以及对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失去信心),“每个人至少应当属于某个拥有共同兴趣的共同体,并且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同伴的肯定”。 [15] 他还写道:“在一个良序的社会中,由于每一个社团都具有稳定的内部生活,社团的多样性往往会降低人们对人类生活前景的差别的关注度,或者说至少降低那些令人不快的关注度。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境况和这些人进行对比:他们在我们的群体之中,或者我们认为他们所担任的那个职位与我们的志向相关。” [16]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逃避——一种掩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被掩盖的差异本身是不正义的差异,那么这就是一种逃避。但与此相反,罗尔斯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提醒去注意各种不平等,那么即使这些不平等是正义的,它们也会带来遗憾和不愉快的对比。罗尔斯说,如果人们形成了这类非比较性的群体,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当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哪一种不平等,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当前的讨论。罗尔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谈到收入和财富的差异,但他主要关注的——也是我在这里关注的——是个人的失败感:一些人最终发现,在某些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上,他们的表现达不到他们有理由想要实现的那种出色程度。作为解决后一个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试图解决由经济差异所引起的不快,非比较性的群体的屏蔽作用看起来就没那么有争议。
无论人们对此如何做出判断,非比较性的群体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我将通过提出与它们相关的一些推测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具体而言,我将推测非比较性的群体会以两种方式与我们的社会最近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急剧增长相关。无论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我认为以下这种想法并不属于其中的一种理由: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所拥有的那些极端财富和收入导致其他社会成员感到地位受损以及失去自尊。首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肯定不会因为我不能按照富豪们已经习惯的那种作风去生活而感到苦恼。也许这只是因为生活已经为我的自尊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支持。因此,对于那些比我穷得多的人而言,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想推测,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地位伤害的那种经济不平等主要发生在以下这些人之间:一边是像我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成功专业人士;另一边则是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尤其是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真正的穷人,并且他们还缺乏教育。我们属于不同的非比较性的群体,这一事实可能会减少地位伤害的影响,但我对这些影响会被完全消除持怀疑的态度。
不过,这一点看起来却很合理:我之所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和超级富豪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差异而感到苦恼,部分原因是我和他们属于不同的非比较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使我陷入地位贫困或能动性贫困,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为我设定任何期望的标准。但是,那种生活的确为他们 设定了一个标准,而这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并不渴望拥有那么多的钱,也不渴望拥有这些钱能够买到的那些东西,比如私人飞机。但显而易见,富豪们的确渴望拥有这些东西。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豪们的比较对象是那些拥有并渴望拥有这些东西的其他人。虽然在群体的外部,不同的群体属于非比较性的群体,但这些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内部比较的场所。
这至少可能与美国最近在不平等方面的部分增长有关,即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增长。对美国高管薪酬水平的批评已经导致确定公司高管薪酬的实践发生了两次改变。 [17] 一是有关高管薪酬的事实变得公开透明很多。二是薪酬委员会越来越多地聘请外部顾问来提供建议,以便决定高管每年的薪酬。这些顾问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提供“比较数据”,也就是说,他们会汇报某些公司的高管薪酬,而相关公司会把自己与这些公司进行对比。
人们本来希望这两项改变——提高透明度和聘用外部顾问——能够防止出现董事会成员偏袒他们的朋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高管薪酬的增长。但现实中似乎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而且看起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对薪酬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措施的一个影响是,公司会把自己与其他同等出色的公司或比自己更出色的公司进行比较,并觉得他们提供给高管的薪酬至少要“跟得上”这些公司所提供的待遇。在我看来,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这些措施巩固了高管们的这种感受,即他们应得 这些级别的奖励;因为他们把有关其他高管的薪酬的公开事实当作一个基准,而这表明了如果人们(成功地)完成他们的那种工作,那么他们应当 得到相同的回报。 [18]
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证,这些关于人们从事某些工作应得多少经济报酬的观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惯例的问题,并且缺乏任何道德依据。然而,在这些社会习俗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觉得他们应得像他们这样的人通常会得到的那些东西,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19]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那些要求和期待得到这些高水平报酬的人的行为,以及那些给予他们奖金和加薪的人的行为。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应得观念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惯例,那么无论人们如何坚定地持有这些观念,它们显然在道德上都没有任何分量。
这可能看起来与我之前所说的内容不一致,因为我之前非常严肃地看待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并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构成了对贫困的重要反驳,尽管我承认这取决于有关社会的普遍态度。但这里不存在任何不一致。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社会惯例都不会导致人们应得这种惯例认为恰当的那些东西。这种基于惯例的应得观念,正是我在涉及富人的期望的例子中所拒斥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某些人未能符合惯例所建立的标准,那么他们需要为此承担代价。富人无法按照他们周围的人所期望的那种作风去生活,这确实会让他们承受一定的代价。但比起这种代价,穷人因忍受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所付出的代价却要严重得多。
总结:在这一章中,我试图描述带有歧视的社会在我们看来有哪些应当遭到反对的地方。我论证道,这种社会的罪恶涉及它不正当地剥夺了一些重要的好处,包括我所说的“团体性的好处”。
我接着解释了经济不平等如何可能造成地位伤害,并且这种伤害就像带有歧视的社会所包含的那种地位伤害一样。这些伤害不仅取决于经济不平等,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对某些好处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普遍态度——涉及评价错误的那些态度。然后我考虑了在以下这种社会中,是否还会有类似的伤害:这种社会不包含上述的评价错误,也不存在歧视,并且实际上还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我把罗尔斯关于非比较性群体的观念看作是避免这种伤害的一种方式。
非比较性的群体这个观念背后的趋势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不管社会有哪些等级,人们主要与具有相似地位的人交往。这种现象在正义和不正义的社会都可能以相同的方式发生。而罗尔斯关注的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分配满足了罗尔斯的正义标准,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相关的等级制就主要涉及以非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不同成功程度。罗尔斯把形成多个非比较性群体的趋势当作一个因素,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社会对自尊的伤害。我已经表明,在不正义并且经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形成非比较性群体的趋势可能会促进不正当的应得和资格观念的发展。
此外,这并不是这种趋势对不平等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富人主要与其他经济水平相同的人交往,那么他们对穷人的生活和需求就更缺乏了解,对他们的困境也会更缺乏同情。 [20] 这会使他们更有可能形成某种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会在第五章来讨论这种观点),从而更不愿意支持那些会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实质机会的政策,并且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在总体上更不愿意满足我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种平等关切的要求。这意味着按照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的那些方式,他们更不可能在公职人员、公民和选民这些角色上发挥适当的作用。
[1] 对于证成某些对待方式而言,统计证据何时以及为什么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对此的讨论,参见Judith Thomson, “Liability and Individualized Evidence”,以及David Enoch, Levi Specter, and Talia Fisher, “Statistical Evidence, Sensitivity, and the Legal Value of Knowledge”。我感谢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和保罗·威特曼(Paul Weithman)向我强调了这一点。
[2] 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386.
[3] 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4] 说这种损失在道德上不相关,并不是否认它们在心理上是强有力的,以及可能在政治上被加以利用从而产生坏的影响。
[5] G. A. Cohen, “Where the Action is,” 10-15, et passim. 科恩特别关注的那种风尚是我们关于正当的态度,即关于个人有资格或没资格去做什么。与此不同,我强调的是关于“什么事物值得重视”和“以什么方式重视它们”的流行观点,并且我也表明这些观点在某个方面(与科恩的提议相类似)是重要的。
[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351-2.
[7] Jiwei Ci, “Agency and Other Stakes of Poverty.”
[8] “Agency and Other Stakes of Poverty,” 128-30.
[9] M. T. Cottom, “Why do Poor People ‘Waste’ Money on Luxury Goods?”
[10] “The Policy of Preference,” 104.
[11] 我在第八章评估了这些不同的应得观念。
[12]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其反乌托邦寓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参见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
[13] 事物具有价值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关于区分这些不同方式的重要性,参见我的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 chapter 2, esp. 99-103。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论证都依赖于这种观点:有些人过度地或以错误的方式来重视某些成就,而且如果他们未能看到某些选项是值得追求的,那么这也是一种错误。但我并没有依赖于这种更强的论点:某些选项具有多少价值以及某个特定的人最有理由去追求哪个选项,这些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实问题。我感谢约瑟夫·费希金(Joseph Fishkin)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14] 约瑟夫·费希金强调了这一点。参见Bottlenecks , chapter 3。
[15] 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388.
[16] 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470.
[17] 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我借鉴了乔希·比文斯(Josh Bivens)和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 Mishel)的相关著述,参见“The Pa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s Evidence of Rents in Top 1 Percent Incomes”。
[18] 例如,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以应得为由为高额薪酬提供了辩护,参见“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19]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变化(即高级管理人员可接受的报酬比率的变化)是近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参见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264–5。
[20] 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所说的“关联社会”(connected society)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避免这些趋势。参见她的“Toward a Connected Society”。
人们通常都把机会平等理解为,个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机会不应当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且普遍都赞成机会平等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却很少提及它为什么很重要。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我的目的是确定机会平等这一理念所涉及的复杂道德观念,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这个议题提供一个道德剖析。我将特别关注支持机会平等的各种考量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平等主义的考量,以及这些考量所涉及的平等观。
因为机会平等与不平等的报酬是相容的,甚至以不平等的报酬作为前提,而且它似乎没有提及我们应当如何限制或证成这些不平等的报酬。所以,在许多平等主义者的眼中,机会平等的名声并不佳。有人可能会说,机会平等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学说;或者有人会说,机会平等是一种神话,它的传播只是为了使不可接受的不平等看起来变得可接受了。人们经常以这种方式来滥用机会平等这一观念,因此我们需要警惕这种滥用。但恰当理解的话,机会平等并不是一种对不平等的证成,而是一项独立的要求:虽然某些不平等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证成,但它们必须满足这项要求才会是正义的。如果这项要求得到认真对待,那么它会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影响。所以,机会平等可能并不应得我所提到的坏名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而要评估这个争论,我们就需要确定有哪些论证在支持机会平等,并进一步澄清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要求。
我将把机会平等看作是对反对不平等的三层回应的一部分。假设有某个人对他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不如他人这一事实提出了反对。我认为要对这个抱怨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就必须涉及以下三个主张:
1.制度证成: 建立一个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2.程序公平: 虽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其他人获得了这个优势,而抱怨者则没获得这个优势,但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3.实质机会: 尽管抱怨者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这一事实没有涉及任何错误的行为。
这些主张构成了我所说的“对不平等的三层证成 ”(three-level justification)。我认为,理解机会平等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理解这些主张的性质和依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制度证成的主张会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有人可能会主张,因为不平等是由人们行使财产权和合同权所产生的,所以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成不平等。或者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给予了人们应得的东西,所以这就构成了对这些制度的证成。但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形式的制度证成,只是为了论述的完整以及形成对比。出于某些理由,我并不认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我会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来讨论这些理由。接下来我将重点关注的是这一类制度证成:它们主张,产生不平等的制度可由建立此类制度所带来的效果而得到证成。
此类制度证成的一种常见形式会主张,一些机构为某些职位的个体(如公司高管)提供高薪,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这些报酬会吸引有才能的个体,从而有助于提高机构的生产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此类制度证成的另一种形式。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特征会使那些过得最差的人受益,并且一旦消除这些特征会使一些人过得更差时,这些制度特征才是正义的。这个证成形式不同于仅仅诉诸提高生产率的证成形式,因为前者具有一个明确的分配要素:不平等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会获得证成,即比起那些在更平等的分配下过得最差的人而言,不平等会使拥有较少益处的人过得更好。这两种证成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主张,设立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是否可被证成,取决于由拥有适当能力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所带来的好处。
我所关注的程序公平是由特定的制度证成推论而来的,并且程序公平的相关标准依赖于这个证成的性质。如果由行使个人财产权所产生的不平等得到了证成,那么唯一的程序要求便是,特定的不平等确实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例如不涉及欺诈或盗窃。而如果证成一个制度的理由是该制度给予了人们应得的东西,那么就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确实是在回应适当类型的应得时,特定的不平等收益才会获得证成。最后,在我感兴趣的那类情形中,如果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机制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此类不平等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那么程序公平就会要求,对这些不平等职位的分配必须确保它们确实会带来这些好处。
因此,如果具有特殊优势的职位之所以获得证成,是因为由拥有某些能力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那么程序公平就会要求,为这些职位挑选担任者所依据的理由必须是他们拥有这些能力。如果这些职位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填补空缺,那么这些职位的运作方式就不符合对它们的证成。我把这种观点称为“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the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procedural fairness)。
当填补优势职位的空缺需要通过某种程序来进行,并且这种程序涉及个人或机构委员会的决定时,例如决定雇用哪些人或允许哪些人进入教育机构,这个理论便能够最直接地加以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公平便要求做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必须和对这些职位的证成有“合理的关联”,即必须和这些职位如何促进其所属机构的目标有“合理的关联”。
鉴于就业是重要的经济利益来源,以及教育是获得许多理想工作的重要途径,上述的情况会涵盖一系列重要的情形,我们自然而然会关注这些情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不是只有这些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才会引起机会平等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人可以通过创办有限责任公司,或者通过获得专利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而变得比其他人更富有。假设对这些机制的证成是基于其所属制度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有些人却通过某种排挤使得另一些人无法利用这些法律形式,并且这种排挤依据的理由也与这些法律形式的经济职能无关,那么我们就能恰当地抱怨这里存在着程序不公平。(正如我们会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如果一些人缺乏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那么抱怨也会是恰当的。)
正如我所描述的,程序公平建立在对某些不平等的证成之上。因此,程序公平似乎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概念——尽管把它包含在内的“三层证成”在这个意义上是平等主义的主张,即它预设了相关的不平等需要获得证成。但在历史上,程序公平的观念却一直是反对重要的不平等形式的依据。
举例而言,许多错误歧视的情形之所以是错误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及我所描述的那种程序不公平。但这不是针对常见歧视的唯一反驳,而且不是所有形式的错误歧视都基于这个理由才是错误的。在那些践行种族歧视的地方,有价值的职位会把不受待见的群体成员系统地排挤在外,也许他们还被剥夺了其他团体性的好处,因为他们被看成低人一等,以至于不适合获得这些好处或职位。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指出的,我们应当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因为它违背了程序公平,而且还因为以这种方式去羞辱他人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在评估申请人时,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和懒惰懈怠在程序上都是不公平的,即便这些做法没有涉及应被反对的羞辱。
“歧视”这个术语可以应用到许多不同的事物上。如果某个政党的成员被排除在法官和其他优势职位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正在遭到“歧视”。对这种做法的反对可以只是在反对某种程序不公平。其他通常被称为歧视的情形则可能没有牵涉程序不公平或羞辱。例如,公共设施无法让残疾人使用,这在广义上就构成了对残疾人的歧视。即使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出一种针对残疾人的羞辱态度,它也应当受到反对,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类平等关切的要求,即它没有以适当的方式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
所有这些情形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错误地剥夺了某些益处或机会。就道德剖析而言,我的目标是找出各种不同的因素,并用它们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剥夺是错误的。我已经提到了三种这样的因素:程序不公平、羞辱和缺乏平等的关切。所有这些错误的行为都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广义上的歧视。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它们是不同的错误行为:这些行为不但可以彼此独立地发生,而且它们之所以是错误的,也是基于不同的理由。
如果机会平等的要求所适用的那些不平等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由拥有相关才能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某些好处,那么“机会平等”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职位,而不管他是否拥有才能。拒绝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不公平的,也不是一种歧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些效果来证成相关的不平等,或者认为证成不平等的理由在于应得,那么择优录用(merit-based selection)就会缺乏依据,因为优点变成了一个不相关的观念。例如,假设指派某人去担任指挥他人的职务,这种做法会解决一些重要的协调问题。但是这个行政职务却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能,那么我所描述的那种程序公平就不适用了。而如果这个职务被认为是值得向往的,那么公平或许就要求我们通过抽签来分配这个职务,以避免应被反对的偏袒。但是,这种公平观与我正在描述的那种公平观却截然不同。
因为这一点在接下来会很重要,所以我必须在此强调一下:与我正在讨论的那种程序公平相关的优点或才能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换言之,哪些能力算作才能(即作为选拔的有效依据),这既依赖于对相关制度的证成,也依赖于那些选拔人才的制度职位的性质以及对那些职位的证成。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才能看作个人的属性,并认为才能的价值独立于利用或犒劳这些才能的社会制度。例如,拥有某种音乐才华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建立某些允许发展和锻炼这种才华的社会制度就会是一件好事。至于哪些能力可以算作音乐才华,在不同的社会里当然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那个社会的音乐传统。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某些形式的音乐才华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传统承认这种价值并允许发展这种有价值的音乐才华,那么这就会是一件好事。
但与程序公平相关的才能却不需要如此,而且通常也不会如此。 [1] 那些才能之所以成为优势职位选拔人才的适当依据,就在于它们具备这些特征(无论这些特征是什么):如果某个人拥有这些特征,那么它们将使得他在相关职位上所发挥的作用会促进这些职位的目标,而正是这些目标为设立这些职位提供了制度证成。 [2] 在少数情况下,这种证成可能与某些能力所具有的独立价值相关。比方说,证成建立一个音乐学校的依据可能是,发展某种音乐才华是有价值的。但这不是普遍的情况。计算机的编程技能可能本身就有价值,也可能本身没价值。而它之所以成为某个职位选拔人才的相关依据是基于这个事实(假定事实确实如此),即让拥有该技能的个人担任那个职位会促进某些其他的目标,例如建立一个使公民能够获得医疗保险的网站。
什么能力才在相关的意义上算作才能,这不仅依赖于制度的目标,而且也依赖于该制度和相关具体职位的组织方式。如果一个职位需要举起重物,那么体力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但如果这个工作是由起重车来完成的,那么体力就不算是重要的能力。同理,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某项工作或大学课程中取得成功,这要求他必须懂法语,那么法语知识就是一种相关的能力。但如果一切事情都是通过英语来完成的,那么法语知识就不是相关的能力。当我说与程序公平相关的才能或能力观念是“依赖于制度”的,我指的正是它们既依赖于那些为制度提供证成的目标,也依赖于该制度为促进那些目标所采取的组织方式。
由此可见,如果某个制度的组织方式要求担任某一职务的个人具备某种特定的能力,但假设它以一种不要求这种能力的组织方式去运作,也能同等地实现它的目标,那么平等就要求它做出这种改变,因为优先考虑具备这种能力的候选人并不具有正当的理由。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假设某个机构的组织方式使得某些工作要求体力,而大多数女性缺乏这种体力,但如果使用机械辅助设备会使得那些工作无须耗费体力,并且该机构能够同等地实现它的目标,那么以女性缺乏体力为由而把她们排挤在这些工作之外,就会是任意的并且缺乏正当的理由。跳过这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与制度证成(这属于我正在讨论的三阶段证成的第一阶段)相关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所谓的产出效率,这些价值还包括制度为个人所提供的从事生产工作的机会。因此,要确定一个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制度是否得到证成,这可能会涉及这些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并且可能会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牺牲产出价值。 [3]
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根据能力来选拔人才不会面临以下这个反驳:当以才能作为依据来分配奖励时,这“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因为被奖励的才能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个人并不能宣称对这些才能“具有功劳”。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具有任意性”这个观念被广泛地误解,也经常被滥用。但按照我对它的理解,当我们说某个特征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任意的,这只是说这个特征本身 并不是对特殊奖励的证成。如果某个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是“道德上任意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条件下,依随(track)这一特征对益处进行分配就是不正义的或在道德上应当被反对,因为我们可能有其他很好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分配。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这句话的当前用法来自罗尔斯。罗尔斯把报酬仅仅由市场结果来决定的体系称为“自然的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并对这种体系提出了反驳。他的理由是,这种体系允许人们的生活前景被那些“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所决定。 [4] 人们经常把这种反驳理解为:这意味着在罗尔斯看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当反对由这种“任意的”因素所决定的分配。但这是一个误解。正如G.A.科恩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差别原则本身会允许某些有利于有才能者的不平等。因此,如果罗尔斯认为,我们应当反对报酬的差异依随着道德上任意的特征,那么他就会是不一致的。 [5] 然而,若按照我所提议的方式来理解道德任意性,则罗尔斯的立场就不会不一致。 [6] 根据差别原则,对拥有特殊才能的个人给予特殊的奖励,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设立这种职位对所有人都有利;换言之,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一个奖励这些才能的制度会带来有利的结果。 [7] 这里并没有把才能本身或才能的稀缺性看成仅凭自身就提供了这种证成。
现在让我来考虑一下,对择优录用的这种制度证成会有哪些可能的反驳。首先,这种证成似乎过度依赖于相关制度所碰巧形成的目标或目的。难道一个制度不会具有一些不恰当地偏袒(或不偏袒)某个群体的目标吗?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某所州立的法学院可能会辩称,由于它的目标是培养对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律师,但招收黑人学生却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没有律师事务所会雇用黑人。 [8] 但这不会对我所提出的观点构成反驳。因为在我的“三层证成”中,第一层次的问题是规范性的问题,即建立包含相关不平等的制度实际上 是否以及如何具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是这个制度如何被看成 具有正当的理由。
程序公平需要依赖于对包含某些不平等的制度的证成,但这种依赖也可能使得选拔标准具有某些灵活性。这不仅与形式的机会平等相容,而且也有利于超越对优点的狭隘理解。比方说,如果社会对某些专业的医生或服务于农村社区的医生具有特殊的需求,那么当某个医学院在决定录取哪个候选人时,除了考虑候选人的预期科学技能和临床技能等因素之外,它还具有正当的理由把那些特殊需求也纳入考虑之中。我在上文提及了某种对法学院政策的证成,但与那种证成不同,这里的证成不会遭受到这种反驳:它构成了一种带来排挤和社会劣等性(inferiority)的实践活动,并且以这种实践活动作为前提。
一些针对女性和少数族群的候选人的平权运动政策,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获得证成。因此,这些政策和我所理解以及捍卫的形式机会平等是相容的。按照我对歧视的定义,当人们普遍相信某些群体的成员低人一等时,歧视就会发生。这会导致把这些群体的成员排除在权威职位和专家职位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不适合担任这些职位或被认为缺乏能力。由于人们关于哪些人能够胜任某类职位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他们的经验中,哪些人通常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反抗歧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以前被排挤在外的群体成员安置在权威职位之上。由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职位上也能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出色。
因此,教育机构作为进入这些职业的重要途径,它们有一个合法的目标去推进这种程序。也就是说,把优先权给予被排挤的群体中那些有能力表现出色的成员,这种做法并没有涉及程序不公平,只要这对该机构的其他目标所造成的损失都被证明是正当的。而这一点是否为真,将取决于这些目标的增量(incremental)损失的严重性。当我们为培养脑外科医生选拔人才时,除了技能和可靠性之外,其他因素应当纳入考虑的程度是有限的。但并非每一个机构目标都具有这么高的边际(marginal)价值。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法学院政策,我所描述的这种政策并没有涉及羞辱: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因所谓的低人一等而被系统地排除在理想职位之外。
支持平权运动的这一理由依赖于这个经验主张,即这种优先政策会产生消除歧视性态度的预期效果(而不是仅仅引发怨恨,或者导致政策的预期受益人被其他人看成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被给予了这种优先权)。这一理由还证明了平权运动的政策只有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才是正当的。因为一段时间之后,要么这种政策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此它将不再被需要;要么它已经被表明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它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
这个例子阐明了两个要点。第一,如前所述,虽然免于歧视的要求和择优录用的要求会互相重叠,但它们有不同的道德依据。第二,这两者都没有要求政策必须处于“(肤)色盲”的状态,或者必须避免使用其他“可疑的分类”。只有当基于种族的决策涉及排挤和低人一等的态度时,免于歧视的要求才会排除掉这些决策。而只有在对种族和其他“可疑分类”的使用与相关制度的合法目标无关时,择优录用的要求才会排除掉这些使用。
另一种针对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的可能反驳是,它似乎不能解释违背择优录用的行为是在错误地对待那个没被选中的人。在种族歧视的情况下,被歧视者之所以受到错误的对待,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个依据是:他基于种族的原因而被判定为低人一等。因此,反对种族歧视的论证建立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不应当遭受这种错误的对待方式。相比之下,如果有人在阅读申请文件时任人唯亲或懒惰懈怠,那么对这些行为的错误之处进行制度性的解释似乎就不能把握到这层含义,即这些实践活动错误地对待了那些被排挤的人。它使得这些违背择优录用的行为看起来只是错误地对待了制度或负责选拔的工作人员的雇主。与此相关的抱怨就只是这个负责选拔的工作人员没有恰当地做好他的工作。
对这个显见反驳的回复依赖于这一事实,即支持择优录用的工具性理由只是更全面的“三层证成”的一部分。这个证成是为了回应某个人的抱怨 ——他抱怨他所拥有的物品比其他人更少。而这个回应是否恰当,则取决于对那三个主张的恰当捍卫,特别是对第一个主张的恰当捍卫,即设立带有特殊益处的职位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证成。支持择优录用的这一理由所具有的制度性特征反映了这个事实:只有当职位的执行方式与对它的证成相一致时,结果的不平等才会得到证成。虽然我们有责任向 受此结果影响的人提供一个全面的证成,但择优录用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步骤,它只是这个全面证成的一部分。(稍后我会对这个反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对制度性理论的第三个关切是,它的涵盖范围可能太狭窄了。例如,假设某类相关职位有空缺,但同等合格的候选人数量却比空缺的职位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从这些同等合格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我们的亲戚或以前的学生,制度性理论似乎也不能对此提出反驳。但是,如果在许多同样有资格获得某一职位的候选人当中,所有被选中的人都是当权者的朋友,那么这看起来应当受到反对。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抱怨这种填补职位空缺的方式不会促进那些为职位提供证成的目标。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对那些被拒绝的人说,任命他们无法同等地实现这些目标。所以,这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正当理由会支持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候选人,而不是其他的候选人。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候选人都不能要求获得该职位。因此,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我所设想的那种选拔方式(涉及偏袒决策者的朋友或政治上的支持者),就不是因为它的结果(被选中的那个候选人),而是因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反对这项政策的理由是,它违背了我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平等关切的要求。这种偏袒之所以看起来应当受到反对,恰恰就在于一些人出于对某个人的利益的更大关切而把职位提供给他。由于平等关切的要求不适用于私人事务,所以如果相关的决定是一件私人事务,那么我们就没理由反对“偏袒”。这种“偏袒”可能是非常恰当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做出选择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设立职位时不会涉及某些候选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抽签看起来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9]
第四个担忧也与这种想法有关,即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过于接近一种以效率作为依据的论证。避免种族歧视并不涉及放弃一个人有资格获得的东西。但是,择优录用是有成本的:它不仅要求负责招聘或录用的工作人员要放弃对亲友的偏袒,而且谨慎地阅读申请材料也需要付出劳动成本。所以,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一个人必须得多谨慎呢?他在选拔的过程中必须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呢?制度性的理由也许会提供这样一个回复: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直到一个更谨慎的过程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会大于额外的谨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在此,额外的谨慎通过促进那些证成设立相关职位的目标而带来了效益。
这个回复看起来并不充分。要对申请人做到公平看起来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例如,使用诸如种族、性别或候选人所在的地区等替代性指标去作为选拔候选人的手段,即使这种做法是高效的,它看起来仍然是不公平的。这一点给了我以下这些启发:在对程序公平的解释之中,制度性理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它才能解释相关的选拔标准。但这种理论忽略了这个事实:人们除了有理由希望获得某些制度职位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和非经济优势,他们还有理由希望作为这些职位的候选人而受到认真对待,并且希望他人的考虑依据的是他们的优点(即由制度决定的优点)。使用替代性指标,甚至没有谨慎地阅读申请材料,这些做法可能都没有给予人们应有的考虑(除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他理由而应当受到反对以外)。
那么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样的应有考虑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特定的情况下,答案可能既取决于制度践行更谨慎的活动所需要的成本,也取决于个体申请人所在乎的事物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仅凭前一种考虑无法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应有考虑的要求既独立于制度效率的要求,也超越了这一要求。就像第二章所讨论的平等关切一样,这个要求看起来既有比较性的因素,也有非比较性的因素。所有人都应当被给予一定程度的谨慎考虑,即使我们很难确切地表明这个程度到哪为止。然而,当超过这种程度的时候,如果某些群体的成员比其他人得到了更谨慎的考虑,那么这种做法也应当受到反对(它违背了平等的关切)。
在本章的开头,我承诺提供一个对机会平等的“道德剖析”——确定它所涉及的各种道德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让我对此稍做总结。我已经表明,这些观念包括:首先,制度所产生的不平等职位如何能够得到证成。我在前文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即程序公平的要求可被理解为此类证成的推论。其次,我审视了这种公平观所涉及的对优点的看法——优点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并考察了择优录用的要求和免于歧视的观念如何互相重叠又有所区别。最后,我还表明,这种观念需要由应有考虑的要求来进行补充。把这些观念合在一起,看起来就解释了程序公平的要求。
但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实质机会的要求以及如何证成这一要求。我将在下一章来讨论这些问题。
[1] 在以下这种情况,它们确实会类似于音乐才华:如果产生不平等的制度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这些制度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并且这种应得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这些制度。我感谢本·巴格利(Ben Bagley)提醒我注意这种可能性。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证,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
[2] 诺曼·丹尼尔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参见“Merit and Meritocracy”,210。丹尼尔斯还指出(218-219):就职位及其报酬而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度证成,而程序公平的任人唯才理念可以和许多不同的制度证成相结合。
[3] 我感谢雷吉娜·斯考滕(Regina Schouten)和约瑟夫·费希金提醒我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4] A Theory of Justice , section 12.
[5] G. A. Cohen,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 158–9.
[6] 科恩考虑了这种替代解释(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 166-7),但他拒绝接受它。科恩的理由是,罗尔斯需要对“道德任意性”采取更强健的解读,从而把“道德任意性”看成是一个支持“平等的基准”(benchmark of equality)的理由,以此来解释在原初状态中如何形成差别原则。但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正如我将在第九章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个基准有着完全不同的依据。
[7] 罗尔斯要完成他对“自然的自由体系”的反驳,还必须论证:虽然奖励某些稀缺才能的实践活动会提高效率,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在某种更平等的实践活动中会获得更多的益处,仅凭效率并不是一种充分的证成。
[8] 罗纳德·德沃金讨论了这个例子,参见Taking Rights Seriously , 230。
[9] 根据其他因素来做出选择,比如雇用一个矮个子或穿蓝衬衫的人,这些都不算是更重视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利益。但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理由来拒绝某些候选人,这意味着没有对那些被拒绝的人的利益给予充分的重视。(参见Frances Kamm’s “principle of irrelevant utilities,” in Morality, Mortality , vol. i, 146。)然而,如果我们之所以将一份工作给予几个同等合格的候选人中的某一个人,是因为他更需要这份工作,那么这种做法就不会遭到我所提及的这些反驳(即违背平等的关切或重视某些无关的因素)。我感谢卡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程序公平关注的是个体竞选优势职位的过程。如果个体要通过这个竞选过程而成为优秀的候选人,那么他就需要拥有教育和某些其他的条件;这些教育和其他条件正是我所说的“实质机会”(Substantive Opportunity)的关注对象。而如果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抱怨他们之所以没能力去竞争优势职位,是因为他们无法充分获取这类条件,那么实质机会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我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项要求以及如何捍卫它?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在美国,即便是一个贫困儿童,只要他努力工作,那么他将来也可能会成为富人。这种说法似乎表明,一种包含了至少某种程度的实质机会的机会平等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或者说至少得到了口头上的认可,甚至许多右翼人士也如此。 [1] 然而,相比之下,人们却很少提及对这个实质性要求的证成。
这种证成将不得不超出我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对程序公平的证成。只要有足够多的候选人具备担任优势职位所需要的技能,从而有助于实现为优势职位提供证成的那些目标,那么对这些职位的证成就不会提供任何理由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培养胜任这些职位的能力。即便一个机构的需求确实提供了理由去投资培养更多合格的申请人,但这种理由也只是基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不是基于正义的要求。 [2]
作为正义的一项要求,某种版本的实质机会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一部分。他对此的表述是:“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 [3] 罗尔斯在没有提供太多明确论证的情况下,就引入了“公平的机会平等”这个观念,而他更喜欢把这个观念解释为不平等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基于类似的理由而支持这样一种要求,即每个人在实质上都能够获得机会;尽管这并非机会的平等 ,因为他认为机会平等是无法实现的。布坎南说,当“城镇上只有一场游戏”时,每个人就必须拥有“公平的游戏机会”。 [4] 布坎南相信,家庭环境的差异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种公平机会的主要障碍。为了抵消这种不公平,他认为良好的全民公共教育和限制代际财富的转移应当是“宪法的要求”,即便这会造成对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一些牺牲。
布坎南心目中的开放性(openness)看起来显然不仅仅适用于人们通过某些程序所竞选的职位(这些程序包括大学录取和就业中的择优录用等),而且也适用于人们通过创业而取得成功等此类事情。限制继承权可以防止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实现后一种成功时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但是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游戏机会似乎也要求贫困儿童至少能够获取某些初始的资金和信贷。正如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安妮·艾斯托特(Anne Alstott)以不同形式所提议的,我们可以通过给所有人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遗产来实现这个要求。 [5]
布坎南为什么会在实质机会上采取这种强硬的立场,从而与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其他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答案是,不同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6] 布坎南是一个契约论者(contractarian)。 [7] 就像罗尔斯一样,布坎南也相信,对于每一个被要求去接受和参与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可被证成。 [8] 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的理想职位没有对所有成员“开放”——不管他们出生在哪个家庭,那么这种证成性(justifiability)的要求就没有得到满足。而如果人们缺乏一个公平的“游戏”机会,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接受并遵守这种“游戏”规则。
我将从以下这两个问题来展开我的论述:支持这项开放性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以及它适用于哪些职位范围?罗尔斯认为,要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成为正义的,这项要求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关于他的正义第二原则,罗尔斯的最初陈述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以便(a)我们能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b)它们所依附的职务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后来他又增加了“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作为进一步的说明,罗尔斯更喜欢用它来解释开放性。这表明,要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成为正义的,开放性的要求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由此可见,这一要求所适用的职位只是那些带有不平等报酬或特权的职位。让我把这种支持开放性要求的理由称为“正义不平等的理由”。
一个更广泛并且要求更高的想法是:如果一些人因遭受歧视或因没有出生在足够富裕的家庭,就被禁止去从事他们有资格胜任并有很好的理由想要从事的那些职业——不管这些职业是否带有特殊报酬或特权,那么这便构成了对该社会的严厉反驳。例如,这些职业包括了艺术家或音乐家等。作为一项实质机会的要求,这个更广泛的要求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除非有胜任资格的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否则他们就缺乏重要的机会去胜任那些要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这无疑构成了对该社会的反驳。 [9] 让我把这种支持开放性要求的理由称为“自我实现的理由”。我之所以提到这两种理由,是因为每一种理由都具有独立的吸引力,尽管较窄的“正义不平等”的理由可能更容易捍卫。 [10] 虽然这两种理由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是相关的,但我将直接关注这个较窄的要求。 [11]
根据罗尔斯的主张,开放性提出了这一要求:“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地谈一谈如何理解才能,以及如何理解“努力”或“意愿”这项动机要求。有了这些澄清,我们就可以转到这个问题:开放性如何与平等和不平等相关?
正如我在之前所提到的,与程序公平相关的能力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概念。如果某个人拥有某种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选拔优势职位的相关依据,那么这便意味着他拥有该职位所要求的那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所产生的效果能够证成该职位的设立。同样,在为学术项目挑选预备人才时,相关的能力就仅仅由这些特征所组成:考虑到这些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这些特征是人们想要在这些项目上拥有出色表现必须具备的特征。
一旦这些职位和教育项目的目标与组织方式确定下来了,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的能力也就明确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某个特定的个体要么具备这些特征,要么不具备,而且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在更大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如果工作或教育项目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意味着实质机会的要求也会有所改变。假设通往重要优势职位的教育项目预设了某些语言、计算机技能或科学训练作为前提,那么罗尔斯的开放性概念就会要求所有人必须都能够获得这些东西。一旦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获得这些技能,那么贫穷家庭的孩子就被阻挡在这些职位的考虑之外。但是,如果获得这些语言或计算机技能是大学相关课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预设的前提条件,那么支持向所有人提供这种训练的这一理由就不适用了。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清楚。但尚不清楚的是,这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概念是否足以理解实质性的机会平等要求,尤其是当这项要求采取了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这种形式——它要求“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 [12] 以这个公式来表述机会平等,看起来是在用能力的概念来为所有人都必须能够获取的教育和其他条件设定标准。而如果一种能力的概念要发挥这种作用,那么它本身就不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教育形式和其他发展条件。
例如,假设一些人觉得抽象推理很容易。因此,他们在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科目上表现特别出色,从而有资格获得那些需要这些技能的优势职位。这似乎与“公平的机会平等”是相容的,因为那些没资格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与那些有资格的人在这些科目上并不具有“同等水平的能力”。但这一结论预设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假设我们发现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方法,无论是特殊的课程、药物还是某种其他的治疗,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其他孩子在抽象推理上发展出同等水平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说我最初描述的教育程序符合“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要求,因为成功的孩子比没成功的孩子在抽象推理上的“能力水平更高”吗?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设富裕家庭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了某些特殊的课程或其他的干预形式,从而克服了这些孩子最初在抽象推理上的缺陷。但是,如果贫穷家庭的孩子没有得到这些好处,那么罗尔斯的公式所表述的那种机会平等看起来就没有实现。
由此带来的结论是:只要能力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那么任何关于两个人处于“同等能力水平”的判断,就都预设了某些特定的教育形式以及其他运用这些能力的条件。因此,把平等的成功前景给予那些拥有同等才能的人,这个观点便不能用来详细说明机会平等所要求的教育形式和其他条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使用一种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概念来避免。但在我看来,没有这样一种概念与对经济制度的证成相关。 [13]
理解罗尔斯的观点的另一种方式是简单地把它解释为,罗尔斯要求儿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依赖于他们的家庭的财富和收入。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在用富人所能提供的教育来为如何确定“同等能力水平”这一观念设定教育标准。它认为,假设我们给予两个儿童充足的动力(稍后我会讨论这个因素),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以及其他现有的发展条件,如果他们表现得一样好,那么他们就处在“同等的能力水平”。
这设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稍后我会考察在一个经济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要满足这一标准所涉及的难题。但是,为所有儿童提供足够好的发展条件之所以是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还因为家庭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 [14] 我们可以通过考虑“意愿”(willingness)的问题来把握这一点,这是我先前搁置的问题。
罗尔斯对“公平的机会平等”的阐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歧义。他首先说:“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 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但他接着阐述了一个更强的条件:如果许多人的心理成长模式由于不幸的家庭环境而导致他们“未能做出努力”,从而没资格去获得那些他们有能力可以获得的优势,那么“公平的机会平等”就没有实现。 [15] 这后一种更强的主张看起来显然是正确的。仅仅缺乏“意愿”或者未能做出努力,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里有陷入某种道德主义(moralism)的危险,这是机会平等观念所面临的重大误区之一。 [16] “同等的意愿”(equal willingness)这一短语可能表明,只要我们能够(真实地)对一个沮丧地提出要求的人说,“如果你更努力地尝试过,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好处,所以你没能获得这个好处是你自己的过错”,那么这就满足了实质机会的要求。这是道德主义的想法,因为它认为,不平等是由穷人的道德过错造成的,所以依据这一理由就可以证成不平等。这里也可能会错误地出现某种应得的观念,它以这种形式呈现出来:努力的人基于他们的努力而恰当地得到了奖励,没有努力的人则由于他们的懒惰而应得痛苦。
虽然这类道德主义和诉诸应得的主张可能具有不少吸引力,但它们都是错误的。 [17] 为了弄清楚它们为什么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以下这种情况会以哪些方式而具有道德重要性,即一个结果是由某个人的选择造成的,或者说它是某个人通过恰当的选择本来能够避免的结果。一种可能的方式涉及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对某个能动者或者对他的行为方式进行道德评价。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做了某件事,那么考虑到他对这一行为及其后果的信念,这便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例如,如果我跟你说我会去机场接你,但因为我想在电视上观看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所以我没去接你。这个事实便表明,比起你的便利和我给你的保证,我更重视这种观看电影明星的快乐。因此,我已经做出了这种选择,这一事实便与你对我的评价和对我们的关系的评价相关。
但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证的,受助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差异并不能证成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所以,一个人的自愿选择会对不平等的结果是否得到证成产生影响,不可能是因为这种选择揭示了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解释。
在我看来,一种更好的解释如下所述。 [18] 人们通常具有好的理由希望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会受到他们在适当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的影响。这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人们在良好的条件下——比如当他们充分了解备选方案并能够清晰地思考它们时——所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因此他们在这些条件下所选择的结果更有可能是他们喜欢和赞成的结果。第二个理由是,比起由其他方式所决定的结果,由人们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礼物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便来源于这个事实(当它确实是事实的时候),即礼物体现了赠送者对接受者的感情;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选择,例如职业选择。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想要对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做出选择,不过这些理由都依赖于做出这些选择时的条件。当一个人不知道替代方案的性质,或者当条件使他不太可能考虑某些有价值的替代方案或不太可能认真对待它们时,选择的价值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的一件事就是,让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取决于他们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做出选择时所采取的反应。对于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比如他们将从事什么职业,这一点尤其如此。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他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未能恰当地做出选择,才使得他没有资格获得某种好处,那么他可能“不会抱怨”他缺乏这种好处。这个人之所以不会抱怨那些提供这种好处的制度,仅仅是因为那些制度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提供这种好处。但是,只有当这个人在做出选择时所处的条件足够好,这一点才是正确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罗尔斯提及“意愿”时其背后的想法。当罗尔斯写道:“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 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不“愿意”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一事实便意味着他们不会抱怨自己没有成功地获得理想的职位。但是,只有当(以及因为)他们在选择不去发展他们的才能时所处的条件足够好,情况才会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所拥有的物品比他们原本想拥有的物品更少,这一事实之所以可被(部分地)证成,并不是基于某种关于他们的道德品质的主张——他们没有付出那种使其应得奖励的努力。 [19] 恰恰相反,这是基于一种关于其他人 (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已经为这些人做了哪些事情的主张:因为 为了让这些人在做出选择时处于良好的条件之下,其他人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所以 这些人不能对此提出抱怨。 [20]
按照这种解释,重要的是一个人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拥有 选择权,而不是他有意识地做出了 选择。如果某个人处在某些(足够好的)条件之下,并且这些条件使得他原本可以通过恰当的选择而得到某个结果,那么这可能就足够了——即便由于他没有注意到他事实上拥有这种选择权,从而导致他在没有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就错过了这个选项。 [21]
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人们——尤其是那些在恶劣条件下成长的人——是道德能动者,即他们能够对其选择承担责任。 [22] 这里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这两个理由。首先,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并没有资格要求获得好的结果:我们必须提供的条件是有限的,而在此之后,需要由人们(他们的责任)来做出自己的决定。其次,即使我们为那些在贫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所做的事情还不够多,他们也仍然是负有责任的能动者,即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不够努力而受到道德批评。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下述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一,他们的选择所反映出的态度是否会受到道德批评;第二,如果社会制度为他们安置的环境使得他们很可能会形成这些态度,那么这些制度本身是否会受到道德批评,即它们是否会因为不符合实质机会的要求而被批评为不正义的。正是未能区分这两个问题才导致了我正在反对的那种道德主义。
要为儿童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以确保他们能够在这些条件下选择如何发展他们的才能,这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种困难不仅仅是由贫穷和贫穷的后果造成的。在一些情况下,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经济因素,或者说不纯粹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可这种困难依然存在。人们可能会对哪些事情发展出“努力的意愿”,这既取决于他们认为哪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也取决于哪些事情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对于在不同社群长大的人而言,这些问题会具有不同的答案。例如,不同于旧秩序的阿米什(Old Order Amish)和罗姆(Roma),在其他社群长大的儿童通常发展出“努力的意愿”是为了实现某些其他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取得社会给予最高奖励的那些成就。情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社群所盛行的态度导致他们不认为这些成就是有价值的,或者不认为这些追求对他们来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举一个不那么极端而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例子:如果一些年轻女性因为她们的家庭相信并鼓励她们相信某些职业不适合女性,从而导致这些年轻女性没有为她们本来能够取得资格的职位而奋斗,那么实质机会的要求就没有得到满足。
与儿童特定的家庭价值观一样,由于儿童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所盛行的态度也会与此相关。我们或许会对以下这种负面的考量耳熟能详:对社会上的种族主义态度和性别歧视态度的一种反驳是(这不是唯一的反驳),它们让被歧视的群体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各种有价值的职业,从而破坏了机会平等。但是,社会态度能够以一种更正面的方式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不违背父母权利的情况下,要让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都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形成关于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和职业的想法,对此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社会可以提供一个更大的环境,使得在此环境之下,孩子们能够考虑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并且这些替代方案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可能的选项。 [23] 这也许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我所描述的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都实现了——职位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向所有人开放”,那么一个人是否会获得某个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就将取决于这个人的能力(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以及他是否选择以必要的方式为这一职位而努力奋斗。然而,我们不应该由此推断出:按照我的观点(或者说,我相信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才能(或能力)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意愿都是个人的特征,并且奖励它们是正义的或恰当的。 [24] 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会对分配正义产生影响,但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规范性的效果,却是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
“才能”的重要性源于对某些优势职位的证成,即一开始设立这些优势职位是有正当理由的;并且它被作为程序公平的依据,也是由这种证成推论而来。而动机作为一种在特定职业中努力工作的倾向,是保持生产力所需要的品质之一;这个特征就像其他形式的才能一样,也是一种得到制度证成的选拔依据。除此之外,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愿意”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这种意愿并不是某种本身值得奖励的个人积极特征。倒不如说,“意愿”的相关性就在于,意愿的缺乏 ——未能利用发展自身才能的机会——能够破坏一个人针对他缺少某些好处而提出的反驳。 [25] 但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意愿的缺乏才具有这种破坏的效果:通过将这个人安置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从而使得他能够通过恰当的选择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对此我们已经为他做了足够多的事情。 [26]
到此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对开放性这个观念的澄清。在以下这两种情况下,某个职业就没有在我们所要求的意义上对一个人开放:第一,他没有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来决定是否从事这个职业;第二,他本该拥有这一职业所要求的能力(这里是在我讨论过的那种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拥有能力”的),但他却没有机会获得发展这些能力所需要的教育。现在我开始讨论开放性与平等的关系。
作为开放性的一项要求,实质机会要求实现某种平等吗,还是它只要求某些条件的满足需要达到一种充足的程度?后者看起来是正确的,因为开放性所要求的只是人们能够获得足够 好的教育来发展自己的才能,以及在足够 好的条件下来选择发展自己的某些才能。罗尔斯要求,那些拥有相同的能力以及具有相同的意愿来发展能力的人,无论他们出生在何种社会阶层,都应该具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取优势职位。罗尔斯的这项要求可能被解释为,人们需要拥有足够好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才能,但对这些条件的获取却不应该依赖于他们的社会阶层。 [27]
然而,对于发展个人的才能而言,什么样的条件才“足够好”呢?回想一下,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依赖于制度的能力,它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教育形式以及其他发展能力的条件。这意味着,只要下述这种情况为真,它就表明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小孩具有能力在某个大学项目或某些职业中取得成功:如果他接受过当前最好的学校教育,那么他就会发展出一个人要取得这些成功所需要具备的那些特征。而从发展这些特征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好的学校教育意味着这些教育与富人可以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一样好。所以在学校教育方面,“足够好”意味着“一样好”。
因此,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开放性。即便每个人都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来决定其职业追求并且都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但一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仍然可能会影响他的成功机会。因为富裕的家庭可以通过贿赂、人脉关系或其他操纵制度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竞选优势职位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程序公平受到了侵犯。我在后面会讨论这种可能性。
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它会影响开放性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开放性对两种条件提出了要求。首先,儿童若想要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具备某些认知能力(如语言技能)和动机倾向(如纪律和志向),所以开放性要求为所有儿童提供幼儿发展这些能力和倾向所需要的条件。虽然这一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阻碍满足这一要求的主要因素是贫困和家庭价值观的多样性,而不是不平等本身。
然而,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如果富人孩子的学校比穷人孩子的学校要好得多,从而使富人孩子能够在高等教育的竞争以及随后的职业竞争中占据主导性的优势地位,那么不平等就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意味着,以下这种情况会违反开放性的要求:如果穷人的孩子接受了富人的孩子所拥有的那类教育,那么他们在竞选优势职位时将会是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由于他们实际上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所以他们无法成为那种候选人。换言之,这些孩子本来能够拥有依赖于制度的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公共教育来满足开放性的这项要求。但考虑到成本以及合格的学校和师资的短缺,我们也很难满足这一点。此外,这里还存在一种教育军备竞赛的风险。在这种竞赛中,富裕的父母会不断地提高开放性所要求的教育水平,因为他们会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的预修课程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经验,以便让他们的孩子在竞选高等教育时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因此,为了确保理想的职位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向贫困家庭的儿童开放,国家看起来必须不断地为所有儿童提高教育水平和早期发展条件的水平,以便达到最富裕的家庭为其子女所提供的那种水平,或者国家必须限制富裕的父母能够提供的教育优势。这无疑构成了一个两难困境,因为前者看起来极其困难,而后者似乎不可接受。 [28]
但值得考虑的是,比起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这一困难是否更多地在于程序公平难以实现。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为优势职位选拔人才的适当标准,既依赖于这些职位的证成目标,也依赖于这些职位的担任者为了促进这些目标所做的事情。出于讨论的目的,让我们假设这些职位已经得到了证成,并且候选人是由于具备在这些职位上表现优异的(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才被选中的。同样,假设某些教育的目的是为这些职位培养人才,并且为这些教育项目选拔候选人的适当标准依赖于这些项目的组织方式,即依赖于它们预设了哪些技能(而不是它们提供机会去获得哪些技能)。
鉴于这种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如果该项目的选拔过程部分依赖于某些与促进这些目标无关的技能,那么这便违反了程序公平。而如果只有富人才有机会获得上述这些技能,那么这种违反行为将格外不正当。但是,即便不存在与经济地位的这种联系,这在程序上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某些技能与教育项目相关(例如使用某一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能力),那么以下这两种做法可能会具有可行性:第一,预先假定这种技能是合格的申请者应当已经具备的技能;第二,将这种技能的培训作为教育项目本身的一部分。现在假设这种技能确实相关,并且这种技能的培训也可以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再假设,当我们对比已经接受过这种培训的候选人和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候选人时,能够辨别出哪些人可能在该项目上表现得更出色。也就是说,这是在假设,除了这种特定的计算机编程技能,我们还能够根据他们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来对他们进行评价。如果这一点为真,那么以下这种做法就会违背程序公平:虽然一些申请人还没有获得这种技能,但我们能够预测到他们在这个项目上会表现跟那些具备这种技能的人一样出色,并且他们还会获得这种技能;可即便如此,那些已经获得这种技能的申请人还是更受到青睐。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当富裕家庭的申请人更有能力获得这种技能时,这无疑违背了程序公平。
现在假设某个教育项目之前一直在常规课程中提供这种技能培训,但它决定要削减成本了,并通过要求申请人在入学之前应该掌握这种技能来“外包”该项目的这部分内容。而这将使得来自贫困家庭的申请人更难通过竞争来获取入学资格。因此,至少在这种培训可以由“内部”提供而不会引起太大的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上述的做法便可能会遭到基于公平的反驳。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相反的方向看起来也同样为真:如果一个机构能够在不牺牲太多效率的情况下而提供某种技能的培训,但它却预设了这种技能(作为资格条件),从而使贫穷的申请人处于劣势,那么它可能就会遭受到反驳。当然,为了避免不公平地使某些潜在的申请人处于劣势,这种教育项目必须承担多少此类的代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我们之前考虑过的另一个问题属于相同的类型,即为了给予申请人应有的考虑,一个机构在审核申请文件时应当保持多大程度的谨慎。
考虑一下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这一特定的情况。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大学录取时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富裕的家庭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这些孩子提供诸如此类的东西:预修课程、出国学习语言,以及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暑期课程。按照我已经提出的论证,只要申请人在大学里也能够获得这些充实项目所提供的技能,那么一种将这些技能视为积极因素的录取过程在程序上就是不公平的。 [29] 以申请人在一系列固定的基础课程中的表现作为依据来对他们进行评估,这种做法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此类的程序不公平。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措施,那么上述两难困境的某个方面就可以避免:我们既不必为所有学生提供这种预科培训,也不必阻止富裕的父母提供这种培训。事实上,我们可以鼓励父母这样做,因为拥有这些额外的技能会让他们的孩子受益,但不会使录取过程对他们有利。但是,如果程序公平没有实现,那么无论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这些好处是多么不可抗拒的一件事,这都是一种钻体制漏洞的方法。 [30]
我刚才提出的这类录用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它会大大地增加那些必须被视为具有同等资格的申请人的数量。正如我之前所提议的,程序公平可能会要求在这些候选人之中使用抽签来做决定。 [31] 这将导致富裕的父母更难在精英机构中为其子女安排位置,从而降低了那种高估此类特定成功的倾向(我在第三章中讨论过这一点),以及降低那种认为此类成功应当以巨大的经济优势作为回报的倾向。
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以及当教育会导向优势职位时,在教育选拔的过程中实现程序公平,这些措施都是迈向机会平等的重大步骤。但这些还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依然留下了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来自很多儿童在幼儿时期的贫穷环境,第二种困难则来自家庭价值观和偏好的差异。然而,这些措施会降低富裕家庭通过支付额外的教育费用而为其子女所提供的竞争优势。剩下的这些问题更多是由贫穷和文化造成的,而不是不平等的产物。
总结一下对机会平等的这个道德剖析:我认为机会平等这个观念是对不平等的“三层证成”的一部分:
1.制度证成: 建立一个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2.程序公平: 虽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其他人获得了这个优势,而抱怨者没有获得这个优势,但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3.实质机会: 尽管抱怨者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这一事实没有涉及任何错误的行为。
我在第四章中论证过,程序公平的要求(即根据优点或才能进行选拔)是对不平等的证成的一个推论,这种证成建立在不平等所带来的福利的基础之上。相关的才能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才能指的是这样一些品质:考虑到 那些职位的组织方式,它们的担任者必须具备这些品质才会使这些职位带来某些福利,而正是这些福利构成了对这些职位的证成。许多程序不公平的情况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错误歧视的例子。但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涉及的羞辱和排挤包含了一种特有的错误,这种错误独立于程序不公平。最后,我论证过,我所提出的“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需要由给予所有人应有的考虑这个更进一步的观念来作为补充。
在这一章中,我把实质机会的道德依据定位在这个观念之上,即社会制度必须对它们所适用的全部对象而言是可被证成的。这种证成性至少要求那些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或许还包括在该社会中人们有理由去重视的其他职业,都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在这里,开放性意味着,除了我所描述的那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这些职业不会基于其他理由而把人们排除在外。
我还论证过,只有当个人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做出选择时,个人的选择才具有相关的道德重要性。而当责任作为道德评价的先决条件时,一个人要在这种意义上对其选择负责,这里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就不同于上述那些足够好的条件。未能区分这两种责任形式导致一些人错误地对机会平等采取了一种道德主义的理解方式。
为人们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对职业追求做出有意义以及具有道德重要性的选择,这一点之所以难以实现是由贫穷和家庭价值观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由不平等所引起的。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平等的确威胁到了这一目标,即结果应当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因为富人总是能够为其子女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似乎只有通过这两种途径才可能被遏制:第一,消除不平等;第二,限制富人能够为其子女提供的东西。我已经表明,如果程序公平确实实现了,并且优势职位的选拔标准不包含对富人有利的不必要因素,那么这一困难便可以得到缓解,即便没有被消除。而这会对那种为了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成功机会所需要的公共教育设置一个上限。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确实是一种对实质机会的严重威胁,因为富人不仅可以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阻碍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好的公共教育。 [32]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机会平等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因为一些人认为它对不平等提供了不正当的支持。人们对机会平等的思考容易陷入很多误区,接下来我将针对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识别出的一些误区进行评论,并以此作为结尾。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即便机会平等实现了,它也不是一种对结果不平等的证成,而只是正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某些不平等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证成,但它们必须满足这个必要条件才会在事实上是正义的。
其次,当机会平等事实上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要以为它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希望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机会平等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即便是程序公平也非常难以实现,并且它的实现程度并没有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么充分。但机会平等不仅仅要求程序公平,它还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实质机会。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避免我所描述的那种道德主义。为自己努力工作而感到高兴和自豪,甚至对自己和其他努力工作的人产生道德上的认可,以及不认可另一些不努力工作的人,这都不是道德主义。这些感受是相当合理的感受。如果某些社会制度承诺奖励努力工作,而某个人为了追求这种奖励已经努力地工作了,那么他自然会感到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些奖励。此外,只要这些制度本身已经独立地获得了证成,那么这种感受就会非常合理。但如果认为这些制度已经得到了证成,并且仅仅因为 穷人不够努力而受到了道德批评,就认为穷人对这些制度的抱怨是得不到证成的,那么这就会是一种道德主义。这种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道德主义的,因为它把焦点放在穷人被假定的(或者即便是真实的)道德错误之上,而忽略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些人是否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来发展他们的才能以及做出相关的决定。
由于这种道德主义的吸引力在心理上具有强大的影响,所以它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人们非常渴望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有资格得到他们已经挣来的那些东西,并且想尽可能多地保留那些东西。不过以下这种观点对这两种利益都构成了威胁:虽然一些人通过某种制度程序挣来了他们的收入,但因为其他人缺乏足够好的条件来参与竞争,所以这种制度程序是不正义的,因此那些已经挣得收入的人应该缴纳更高的税收来纠正这种不正义。道德主义提供了一种逃避这一结论的方式,它允许人们继续相信他们的收入是合法的,并且不必相信他们被要求做出任何牺牲。指出这种思路所涉及的哲学错误可能不会损害其广泛的吸引力,但这仍然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1] 不过,也有一些人拒绝实质性的机会平等。哈耶克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他接受了一种较弱版本的形式机会平等,这在他看来意味着没有歧视以及一种“职业对才能开放”的政策。例如,他写道:反对由家庭财富差异所导致的儿童前景差异,并不会比反对由不同遗传天赋所引起的差异更有理由,因为后者也是儿童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94)。他可能认为,由于这两种因素都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一个儿童对后者(才能)所应得的功劳并不会比前者更多。我在第四章已经解释过,把更多的报酬给予那些有“才能”的人,这种做法的合法性不需要依赖于这个假定,即他们应得这些报酬或他们能够“宣称”对他们的能力“有功劳”。罗伯特·诺齐克也拒绝这种强硬形式的机会平等(Anarchy,State and Utopia , 235-9)。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平等来自个人通过行使其财产权所做出的选择,那么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成不平等。
[2]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提出了这个论证。他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会带来“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这便构成了对中小学教育开支的证成。参见Capitalism and Freedom , chapter 6。这是一个支持资助公共教育的好理由,但不是唯一的理由。
[3] A Theory of Justice , 73.
[4] “Rules for a Fair Game: Contractarian Note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布坎南还写道:“恰当理解的话,即使作为一种理想,‘机会平等’也必须通过以下这种方式来定义:不管对于参与者的特定情况而言,何种‘游戏’才是最合适的,‘机会平等’意味着参与者在创造价值的能力上缺乏某些粗略的、可能不可通约的重大差异。”(P. 132)
[5] 参见Atkinson,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 169–72和Ackerman and Alstott,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他们都把这个想法归功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土地的正义》(Agrarian Justice )。我们越重视这种创业的成功,就越会加强这些措施。约翰·托马西(John Tomasi)认为罗尔斯等理论家不够重视这种类型的机会。参见Free Market Fairness , 66, 78, 183。但托马西的回应方案却是对经济自由采取某种形式的宪法保护,而不是采取措施来保障利用经济自由的能力。
[6] 哈耶克似乎主要是一个后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他也用后果主义的理由(他称之为“权宜之计”的理由)来为自由市场辩护,尽管哈耶克表示他同样“把个人自由的价值作为无可争议的伦理预设”。参见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6。
[7] 他的文章的副标题是“分配正义的契约论札记”(“Contractarian Note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另外,布坎南在《一种对罗尔斯式的差别原则的霍布斯式的解读》(“A Hobbes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wlsian Difference Principle”)中说,他和罗尔斯“共享着准康德式(quasi-Kantian)的契约论预设,而不是边沁式的效用主义(utilitarian)概念”。在他和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合作的《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一书中,布坎南评论说他和马斯格雷夫“基本上”都是契约论者,并且他说“我根本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效用主义者”。关于布坎南与罗尔斯之间漫长且令人尊敬的思想通信,参见Sandra J. Peart and David M.Levy (eds), The Street Porter and the Philosopher , 397-416。
[8] 对于那些被要求去接受某些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需要在什么意义上得到证成,人们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按照我的看法,道德和正义的原则是由这两种理由的相对强度来决定的:一些人有某些理由来反对某一方案给他们带来了负担,其他人则具有另外的理由来反对那些没有包含这些负担的替代方案。(参见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 chapters 4, 5。)布坎南关于证成的看法可能缺乏这种明确的比较性质,但它建立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之上:因为不同的原则会以某种方式对人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所以这些影响方式给人们提供了理由。(参见脚注7中所引用的布坎南的著作。)相反,杰拉德·高斯(Gerald Gaus)认为,一个制度或政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被证成的:在相关生活的所有方面,比起没有管理规则,每个公民都有充分的理由更愿意接受这个制度或政策。他认为,相关的理由建立在每个公民实际的规范观点之上,包括公民对道德和正义的实际观点,而不管这些观点可能是什么。一些公民可能在其他人能够要求他们提供什么东西这一问题上持有某些最低限度的道德观点,而这会导致在国家必须或可以提供什么东西这一问题上得出相应的最低限度的结论,因为高斯的一致同意要求(requirement of unanimity)赋予了这些公民否决权,使得他们能够否决任何提出更高要求的方案。(参见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 chapter 6, esp. 363-6。)
[9] 乔治·谢尔(George Sher)为这种更广泛的要求提供了辩护,参见Equality for Inegalitarians 。他写道:“国家有义务让每一个公民都尽量能够有效地生活。”(第157页)在这里,“有效地生活”意味着“接受那些我们事实上有理由去追求的目标,构思以及采纳某些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并且以某些有效和灵活的方式来执行这些计划”。如前所述,这是一项非比较性的要求,并且这项要求为不同的个体所提供的资源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能力。不过,某种平等的要素会通过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平等关切的要求而加入进来。这正如谢尔所说的:“我们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的利益同等重要。”(第94页)
[10] 诺曼·丹尼尔斯似乎诉诸了这个更广泛的概念。他说在他的论证中,机会平等要求医疗服务必须成为公平的机会平等的一个必要条件。丹尼尔斯说,人们必须能够获得对疾病的治疗,因为“与一个人所处社会中的正常机会范围相比”,疾病“破坏了他能够利用的机会”。在他看来,“正常的机会范围”指的是,考虑到“该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物质财富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合乎情理的个体有可能会为他们自己制订的那一系列‘人生计划’”。(“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Decent Minimums,” 107.)
[11] 罗尔斯的某些话暗示了这种更广泛的要求。例如,“每一个具有相似的动机和天赋的人,都应当拥有大致平等的文化前景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相同能力和志向的人,他们的期望不应当受其社会阶层的影响”(A Theory of Justice , 63)。如果把以“文化和成就”作为衡量标准的认可(recognition)也纳入“自尊的社会标志”(它属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基本益品”)之中,那么这两个理由之间的差异就可能会被弥合。但是,这类认可的不平等并不具备(或者说,我认为不需要)我所假定的那类制度证成,即诸如收入、财富和“带有权力和特权的职务”等其他社会基本益品的不平等所要求的那类制度证成。
[12] 约瑟夫·费希金在《瓶颈》(Bottlenecks )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尤其在第二章中。我极大地得益于费希金的讨论。
[13] 费希金强有力地论证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概念。参见Bottlenecks ,chapter2。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残疾”(disability)这个概念。如果某个特征使其拥有者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更难以采取他们有理由想要的那些方式去发挥作用,那么这个特征在一种重要的道德意义上便是一种残疾。可能有某种残疾的概念,例如“物种正常功能的缺失”,它不依赖于制度,并且不以这种方式依赖于特定社会的性质。但我认为,这样一种概念在道德上并不重要。一个人缺乏他所属物种的典型特征,这一事实只有以某种方式干扰了他有理由在乎的事情,它才在道德上是重要的。从残疾依赖于制度也依赖于社会这两点可以得出,我们在原则上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防止由残疾引起的机会不平等:要么通过改变社会以便使得重要的社会角色不需要原来那些相关的特征,要么使个人有可能避免拥有这个“残疾”特征。
[14] 经济阶层的差异和传递给儿童的态度的差异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育儿策略与工人阶级或贫困家庭的育儿策略在向儿童传递不同优势方面有何不同,参见Annette Lareau,Unequal Childhoods 。
[15] 罗尔斯提及“做出努力的意愿”取决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那个段落很具有代表性。参见A Theory of Justice , 64。
[16] 塞缪尔·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提出了这一点,参见“Choice, Circumstance, and the Value of Equality,” 220ff。
[17] 我会在第八章提出论证来反驳这种诉诸应得的主张。
[18] 更充分地阐述这种解释,参见我的“The Significance of Choice”和chapter 6 of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
[19] 之所以只是部分证成,因为这一点也是必要条件,即产生相关不平等的制度应当具有正当的理由;也就是说,我的“三层证成”的第一层证成应该得到满足。
[20] 谢尔要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取“有效生活”的工具,这一要求包含了一个类似的,甚至更强有力的意愿观念。他要求公民应当处在好的条件之下来决定采取哪些目标(参见Equality for Inegalitarians , 157),并且“为了避免底层人员把努力视为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国家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一系列的资源和机会,从而使得如果他确实努力的话,就会有一个合理的成功机会”。(第150页)
[21] 更多的讨论,参见我的“Responsibility and the Value of Choice”。因此,在我所提供的这种解释之中,选择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于其在运气平等主义的观点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运气平等主义的观点,如果对平等的偏离是由人们的实际选择造成的,那么这种偏离便可得到证成。对运气平等主义观点的批评,参见Sher, Equality for Inegalitarians , 29-34。
[22] 例如,就像诺齐克所指责的那样。参见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214。
[23] 约瑟夫·费希金提出了这一点。他强调机会平等(他称为“机会多元主义”)的一个条件是社会要体现出某种多元的价值观。参见Bottlenecks , 132-7。这看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多元化社会的可欲性似乎与机会平等的观念是相互分离的。但我刚提出了某种对罗尔斯的“意愿”条件的解释,这种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联系。
[24] 费希金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参见Bottlenecks , 31。
[25] 努力似乎能够以其他方式来证成更多的回报,我在第八章中对这些方式进行了讨论。
[26] 以“选择的价值”来分析“努力的意愿”的重要性,这也解释了费希金对“起跑门”(starting gate)体制和他所说的“大考社会”(big test society)的反驳。在“大考社会”中,儿童会因其早期的表现而不可挽回地被分成不同的教育路径和职业轨道。然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没有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来做出这些重要的人生选择。参见Fishkin,Bottlenecks , 66-74。
[27] 罗尔斯写道:“每一个具有相似的动机和天赋的人,都应当拥有大致平等的文化前景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相同能力和志向的人,他们的期望不应当受到其社会阶层的影响。”(A Theory of Justice , 63.)
[28] 机会平等会提倡采取这种措施,这正是哈耶克对机会平等所提出的反驳之一。参见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91-3。
[29] 在就业方面,这种不公平的例子包括对某种工作实际上不需要的能力的测试,以及优先考虑那些通过无薪实习而获得经验的申请人,因为只有富裕的申请人才能负担得起这种无薪实习。
[30] 这与托马斯·内格尔在《平等与偏袒》(Equality and Partiality )第十章中提出的观点有关。内格尔观察到,父母想为其子女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种动机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构成不平等的根源。在家庭的内部,父母通过教学、辅导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而在不同的程度上促进了孩子的前景。在家庭之外,父母可能也会想通过“人脉关系”和其他钻体制漏洞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孩子,以便让他们在竞选优势职位的过程中拥有出色的表现。内格尔说,后一种对平等的威胁可以受到规范的约束,从而禁止父母以这些方式来为其子女谋取优势。但社会的运转依赖于父母在家庭内部对他们的孩子有所作为。因此,社会需要鼓励这一点,而不是阻止它或限制它,并且把这种阻止或限制当作一种促进平等的方式。
我所建议的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之间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内格尔所描述的这个问题。如果程序公平实现了,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父母尽力促进其子女的教育和发展。但如果程序公平没有实现,并且父母所提供的额外培训和改善会对选拔过程产生不恰当的影响,那么为子女提供这些福利就会干扰程序公平。因此,这种做法就跟试图通过“人脉关系”来为子女谋取好处的做法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阻止的行为。
[31]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许多社会广泛地使用抽签来分配此类稀缺物品。参见Local Justice 。
[32] 正如我在第二章和第六章中所讨论的。
在许多人看来,经济不平等显然正在对我们的民主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等人的最新研究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吉伦斯的研究表明,在富裕公民和贫穷公民有着相互冲突的偏好的那些问题上,政治结果与富人(那些收入在前十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密切相关,而与穷人(那些收入在后十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完全无关。 [1] 他说中等收入人群的偏好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几乎和底层人群一样小,并且这些影响力上的差异与经济地位相关,而不是与教育水平相关。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通过研究参议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次国会中针对最低工资、公民权利和预算问题的投票,他发现,比起中等收入选民的观点,这些投票与高收入选民的观点更密切相关,而与低收入选民的观点根本无关。 [2] 他认为,尽管穷人比富人更少去投票或更少去联系议员,但这种倾向无法解释上述的发现。在这些分析中,富人不仅仅指的是那些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吉伦斯关注的是收入在前百分之十的人,而巴特尔斯则将2006年收入超过六万美元的人视为高收入人群。
我在这一章中关注的是这个规范问题:如果情况确实如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为什么应当受到反对呢?具体而言,政治制度的公正性(fairness)提出了哪些要求,经济不平等又会如何干涉它呢?
一个自然而然的回答是:吉伦斯和巴特尔斯的研究表明,富人对政治结果的影响要比穷人大得多。罗尔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某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称之为“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并认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不能阻止“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以及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 [3] 尽管罗尔斯确实指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能导致一个“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发展壮大,并且这个阶级会“感到被忽视,以及不能参与公共政治文化”,但他的主要反对意见并不是说,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不能像其他社会的公民那样投票或参与政治。 [4] 倒不如说,罗尔斯反对的是,这种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从而损害了这些活动对贫困公民而言所具有的“价值”(worth)。他说:“无论公民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如何,政治自由对所有公民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必须大致平等,或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充分地平等,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担任公职以及影响政治决策的结果。” [5]
如果比起穷人而言,政治的结果更有可能符合富人的意见或利益,那么这也许表明这种政治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缺陷。但我认为,只有其中某些缺陷能被恰当地理解成影响力的问题,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会有所不同,而我们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区分。我接下来的目标是确定这些不同的缺陷,并考虑它们是如何由经济不平等造成的。
罗尔斯指出,“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个观念与他的“经济机会的公正平等”观念非常相似,有时候他还会以一种使这个相似之处更加明确的方式来表述前一种观念。例如,他说以下这种情况,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便实现了:“无论公民处在哪个经济和社会阶层,那些具有相似天赋和动机的公民都拥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获得权威的职位。” [6] 但与“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这个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并非是完全对应的,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探究。不过这个相似之处却可以作为考察政治公平的有益起点,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第四章和第五章对经济机会平等的分析。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区分了机会平等的程序方面和实质方面。程序方面由这些制度组成:它们界定了某些优势职位以及这些职位所具有的权力和奖励。如果这些职位获得了证成,并且它们在实际上的运作方式符合对它们的证成,那么程序公平就实现了。而这些制度所界定的优势职位之所以获得证成,是因为当拥有适当资格的个人来担任这些职位时,设立这些职位会带来好的结果。此外,如果选拔机制实际上是根据这些资格来挑选候选人的,那么这些选拔机制也就得到了证成。然而,即便这种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恰当地进行运作,但也只有当它们所创造的职位对所有人都开放时,它们才可获得证成。这一点对某些背景条件提出了要求,例如它要求人们能够获得那些发展相关资格所需要的教育。我之前把这一点称为“实质机会的要求”。
因此,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经济机会平等。首先,如果富人能够设立某些得不到证成的优势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只对他们有利,或者如果富人能够以某些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那些得到证成的职位的选拔过程——因为这些方式会偏袒他们或他们的子女,那么经济不平等就会干扰到程序公平。其次,如果穷人无法进入学校或无法获得与富裕的候选人竞争优势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那么不平等则会干扰到实质机会。
政治公平的实现同样也要求恰当运作的制度和适当的背景条件。但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支持它们的理由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一样,政治公平所关注的制度也创造了带有特殊权力的优势职位,并且界定了个人竞选这些职位的机制。但这些制度同时也是做出权威性的政治决策的机制,它们制定了一些要求公民去接受以及遵守的法律和政策。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制度所界定的优势职位包含了做出这些决策的权力,即批准法律法规、做出司法决策和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
正如我已经表明的,经济机会平等所关注的优势职位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由拥有适当资格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好的结果。对于政治制度所界定的某些职位来说,例如法官或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职位,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职位应该通过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来填补空缺,正如在美国,很多法官的职位都是如此。
但立法者、市长或总统等其他职位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由合格的个体来行使这些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会带来好的效果,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成这些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人是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这一事实同样也至关重要。因此,让这些人行使这些权力是我们实现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我们针对该做什么事情——例如该修建什么样的道路,提供什么样的学校和其他福利,以及如何支付这些费用——采取集体决策的一种方式。 [7]
对这些权力的证成依赖于许多不同的事情。首先,它依赖于选拔候选人的程序结构以及行使权力以做出权威性决策的程序结构。为了让某人当选公职人员具有合法性,选举就必须具备恰当的形式。例如,如果某些公民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或者他们的选票被党派不公正地划分选区(partisan gerrymandering)所稀释了,或某些公职的候选人被排除在考虑之外,那么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但是,即便是公平选举所授予的权力也要受到限制。因此,制度要获得证成就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对这些权力进行限制,例如必须保护公民的权利。
不过,即使政治制度的组织方式在程序上是公平的,它们所授予的权力仍然依赖于是否存在着适当的实质性背景条件。即便某些公民拥有选举权和其他参政的权利,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使用那些要成为公职的候选人或进入公共论坛所必需的手段,从而做不了这些事情,那么选举所具有的使权力合法化的力量就会受到损害。
稍后我会继续讨论政治制度的证成性所需要满足的这些条件,以及不平等可能以哪些方式破坏它们。不过我目前关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证成结构和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的证成结构之间的差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尽管优势职位涉及某些自我实现的机会且这些机会有利于优势职位的担任者,但对这些职位的证成主要依据的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给担任者所提供的机会。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则是一些得到证成的集体自治机制。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在制度的证成性和使公民能够参与其中的背景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同的关系。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程序公平的标准具有“自上而下”的理由或制度性的理由:因为个人必须具备某些品质才能够在优势职位上发挥作用,从而符合对这些职位的证成,所以优势职位必须依据这些品质来挑选候选人。但这种理由并不需要扩展到实质机会的要求。如果来自富裕家庭的合格候选人足以担任这些职位,那么我们就缺乏任何制度性的理由来确保其他人有机会成为合格的候选人。支持实质机会的理由则是一个独立的、“自下而上”的问题,它建立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之上:人们不应当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但就政治制度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如果缺乏适当的背景条件意味着许多公民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那么政治制度就不是民主自治的适当机制。因此,政治制度的公正性不止提出了某些结构上的要求,而且对这些结构要求的证成还会扩展到对提供背景条件的证成——这些背景条件是人们要参与这些制度所必不可少的。
政治公平和经济机会平等之间的另外两个差异也值得注意。第一,广泛的立法权力会允许政治制度改变其合法性所依赖的条件。它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一是改变自身的程序,正如在立法重划选区(legislative redistricting)的情况下便是如此;二是维持或放弃维持那些必要的背景条件,例如这些背景条件包括人们能够接受教育以及获取政治参与的手段。第二,人们重视投票权以及重视以其他方式参与政治的理由之一是,这些权利既是使必要的背景条件更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手段,也是使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更有可能获得证成的手段。
在阐述了经济机会平等和政治公平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后,让我回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政治公平的要求这个问题上来。我引述罗尔斯的那段话似乎表明,政治自由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应被理解为,人们在利用这些自由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件事上具有多大的成功可能性。我想追问这是否是对政治公平的最佳解释。为了清楚地解决这个问题,区分罗尔斯所提到的两种不同的成功情况是很重要的,即“获取权威职位”和“影响政府的政策”。
罗尔斯所关注的优势职位大概既包括了法官这样的职位,这些职位对个人的选拔建立在实质标准的基础之上;也包括了那些选举职位,它们的相关标准在于一些人通过恰当的程序而当选。尽管有些候选人可能比其他候选人更有资格担任公职,但民主选举的一部分理念就在于由选民来决定选择哪一个候选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得很糟糕。但是政治体制的公正性并不会仅仅因为下述这一事实而受到质疑,即有些人不太可能获得选举职位,因为大多数人(无论明智与否)更喜欢其他的候选人。
由此可见,公平对选举职位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能以成功的可能性来加以界定,也就是说,不能以实际上获得职位的可能性来加以界定。选举的成功在于说服别人为某个人投票。因此,这种成功严重地依赖于别人的实际反应。假设我们因为提出劣质的论证而无法说服我们的公民同胞来支持我们,或者即便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思想封闭或不理性,从而没有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实际上无懈可击的论证,但这些情况都不会违背政治上的程序公平。虽然以“成功的可能性”作为公平的标准会造成这种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平等的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政治公平似乎并不要求所有潜在的候选人都具备“充足的 成功可能性”。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罗尔斯所提到的另一种情况,即“影响政府的政策”,至少当人们是通过选举的程序来产生这种影响时,情况便是如此。
由于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主张,政治公平所要求的并不是人们对于影响政策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而是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 来产生政治影响。 [8] 在有些人看来,这意味着一个人获得公职或影响政策的成功可能性不应取决于他的经济和社会阶层。但如何解释这种可能性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富人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大多数选民都特别崇拜有钱人并且相信他们的判断,那么这并不表明这些政治制度是不公平的,无论这可能表明这些选民具有什么样的智慧。然而,如果富人之所以更有可能获得公职或影响政府的政策,是因为更多的财富使得他们更有能力竞选公职以及以其他方式参与政治(例如支持其他政治运动),那么这将表明这些政治制度是不公平的。
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科恩关于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平等的观点应被理解为,人们应当能够平等地获取(equal access to)某些手段 ,即那些人们通过选举程序来获得公职以及更广泛地影响政策所需要的手段。 [9] 例如,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我们可以通过保障每个人有权利使用相同时间的麦克风,来确保人们实现参与权的公平价值,尽管这并没有保证任何人具有任何特殊的成功可能性。
然而,这种解决办法依赖于上述特定情况所独有的某些特征:第一,在会议上发言是人们用来影响别人的意见的主要手段;第二,允许每个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发言是切实可行的。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政治影响力的情况并不具备这些特征。我们没有任何切实可行以及合理的方式能够让每个公民在相同的时间内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关注,甚至只是得到重要公职人员的关注。此外,人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个人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在此仅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演讲、出版、撰写博客文章、给政治公职人员写信等。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相同数量”的此类活动,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可行性。
另一种说法主张,公平所要求的是贫穷的公民和富裕的公民都应该能够获得充足的 手段来影响选举的进程。我们可以把“充足的手段”定义为这种能力:能够使自己的竞选情况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并被他们纳入考虑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是由选举具有使权力合法化的力量这种观念推论而来的。如果选民不知道B是候选人,或者他们无法知道B所具有的优点,那么选举中的投票实际上并不表明他们更支持A而不是B。
然而,这种充足的概念太弱了。即使几乎所有的选民都知道某个人的参选资格,并且知道他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知道他声称拥有的优点,但其他候选人也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的信息被更频繁地重播并且主导着主要公共媒体关于选择候选人的报道,从而获得了胜利。人们愿意在政治竞选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他们想必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赢得美国大选的候选人几乎总是那个在竞选上投入更多资金的人,这些事实都证明了那些进一步的报道(而不仅仅是被别人知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10]
所以,按照我对“充足”所采取的那种最低限度的定义,即使所有公民都能够获得充足的 手段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参选资格,那些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的富裕公民依然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来影响选举的结果。 [11] 虽然我们很难定义何谓“拥有平等的手段来影响他人”,但如果某些人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这种能力会导致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手段来影响政治的结果,那么这看起来显然会引起反对。事实上,要理解罗尔斯关于“同等的成功可能性”的评论,这看起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它不是一种在字面意义上关于可能性(概率)的主张,而是一种关于获得产生政治影响的手段的主张;也就是说,虽然富人有能力在政治竞选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这种能力不应给予他们某种决定性的优势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以及影响更广泛的政治结果。
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是在说:选举的结果应该由针对“问题”进行理性说服的方式来解决,并且一旦有些人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来重播他们的信息,或者采取非理性的说服形式,那么这个过程就受到了扭曲。基于这个理由,如果某些政治制度的特征会破坏审议环境的质量,那么它们就应当受到反对。但是,当前的观点却与此不同:无论选举的结果取决于理性的论证,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由非理性说服的争辩所构成,只要某些人有能力在宣传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这会导致他们在选举上拥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这种情况就应当受到反对。 [12]
为什么我们应当反对富人拥有这种优势呢?我们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是因为它意味着贫穷的公民被剥夺了影响选举结果和政治决策的机会,并且导致富裕的公民对选举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拥有不公平的影响力。但仅凭这一点,这种回答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如果一些人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并且属于根深蒂固的(entrenched)少数派,那么他们同样也无法影响选举的结果,但这一点似乎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引起反对。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根深蒂固的少数派群体之所以缺乏影响力,仅仅是由选民的意见造成的,因此这在多数票决定的制度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仅仅由于许多选民崇拜和信任富人,就可能会让富人拥有优势。)无法平等地获取那些可用来影响他人的手段会导致人们拥有不同的机会来产生影响,并且要消除由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机会差异可能会很困难,但这种做法与多数票决定的制度并非不相容,它甚至可能会强化这种制度。其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歧具有特别广泛的影响。在一个问题上属于少数派的人可能在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上属于多数派。(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根深蒂固的少数派就更令人不安了。)但在富人和穷人产生分歧的那些问题上,例如提供重要的适当公共教育所需的税收水平,处在失败的那一方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那些当选的公职人员本身就很富裕,那么政治决策在总体上将被他们特有的经验和利益所塑造。即使撇开其他人的影响,他们也很可能不太了解穷人的需求,并且会对这些需求做出更少的回应,从而更有可能导致平等关切的失败以及没有履行非比较性的义务。
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描述的现象确实表明了影响力的机会不平等。 [13] 但在评估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体制的公平时,我们不应只关注公职人员对不同公民的偏好的回应。对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制度的运作,这里还存在着其他的反驳。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有一些标准会限制民主选举的代表有资格去做哪些事情。例如,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是不合法的,即便某个体制的选举程序是公平的,并且这些法律在该体制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投票支持此类法律的立法者将违反那些界定他们的义务的规范(norms),而一个政治体制必须把这些规范包含在内才能够获得证成。如果某种影响力会导致立法者违反这些规范,那么它就应当受到反对。但这种反对不是基于影响力的不平等,而是基于这种影响力所造成的政策。这个观点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只要立法行为具有实质性的标准,那么这个观点就能适用。以下这三类情况看起来就具有这样的标准。
第一,政府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某些福利,并且这些福利的供应至少要达到某种最低水平。这些福利包括治安保护、对避免错误定罪的保护,以及基础教育、饮用水、铺设的道路和适当的卫生设施等公共服务。如果立法者或其他公职人员未能为部分市民提供这些福利,那么他们就会因此而受到批评。但这里的指责并不是说公职人员没有受到某些公众的意见或偏好的影响,而是说他们没有对由这些公民的利益提供的理由做出应有的回应。
第二,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在超出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公职人员没有提供任何好的理由就为某些公民提供比其他公民更高水平的福利,那么这也应当引起反对。但这种做法之所以引起反对,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影响力的不平等,而是因为它涉及某些公民的利益 比其他公民的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从而违背了平等关切的要求。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涉及军事政策的决定或建设公共建筑的合同,立法者和其他公职人员有义务以公共利益的考虑作为决策的导向,而不以特定公民的利益作为导向。如果某些决策没有这么做,并且分配资金的目的是让特定个人或特定地区受益,那么这些决策就会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有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
在所有这三类情况下,按照我之前对“程序”所采取的那种强健意义上的定义,这些反驳都属于程序性的反驳。它们所提出的指责是,政治制度必须以某种方式运作才可得到辩护,但这些政治制度都没有以这种方式来运作,因为公职人员的决策并没有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因此,这些情况类似于在程序方面违反经济机会平等的那些情况,例如负责招聘或大学录取的工作人员未能挑选出最合格的申请者。(相比之下,由于富人有更大的机会来影响选举,从而使得不平等会干扰政治公平,这种情况类似于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所说的对实质机会的违背。)
在违反我正在讨论的这类程序标准的情况下,影响力 的观念只是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违反行为会发生,而没有用来解释为什么它们应当受到反对。这些违反行为可能是由竞选的捐助者向立法者施加压力造成的,而且捐助者会要求立法者采取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违反程序公平的行为可能是由富裕的父母为其子女寻求特殊照顾造成的。但不管这种失败是由这类影响造成的,还是由集体忠诚、单纯的懒惰或疏忽造成的,对此的根本反驳都是相同的,即一些人未能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而当失败是由其中的某一种影响造成时,这种影响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仅仅是因为它导致决策者没有按照相关的依据来做出决策,而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比其他人能够产生的影响更大。
在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讨论的那些情况中,许多情况看起来都涉及对这类标准的违背。吉伦斯考虑的政策问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向海地派遣美军,要求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允许同性恋者参军,等等”。 [14] 巴特尔斯的数据则关注的是参议院关于以下这些问题的唱名表决(roll-call votes):提高最低工资,民权法案是否应涵盖就业歧视,将国防开支的资金转移到援助穷人的项目上,等等。 [15] 在这些情况下,立法的决策似乎应当符合某些包含平等关切在内的具体标准。
然而,我正在考虑的这类实质性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某些政策问题。我们可能会说,在这些情况下,政治的决策就应当反映公民的偏好,因此应当受到公民偏好的影响,并且如果一些公民的偏好比其他公民的偏好受到更大的重视,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正当的。例如,由于公民对于哪些计划会促进共同利益这个问题必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当基于促进共同利益的理由来决定哪些计划会得到证成时,立法者就应当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公民的观点做出回应。而基于我一直在讨论的理由,如果立法者支持某些有利于特定个体的政策,而不是那些促进共同利益的政策,那么这种做法就应当遭到反对。
同样,我在第二章中提出,政府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提供某些公共福利(例如铺设道路)而不会引起反对。不过,一旦确定这种水平的政策被选定了,如果政府为富人的社区或市长朋友的社区更频繁地铺设道路,那么这种做法便违反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但是,也许某个城镇上的穷人更愿意使用较少维修的道路以便降低税收,而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富人则更愿意拥有更好的道路。如果由于城镇议会的成员本身就很富有,或者因为富人对他们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捐助,由此导致议会的成员忽视了穷人的偏好而投票支持增加铺路的预算,那么这种做法便违反了对公民的偏好作出回应的要求;即便就这种特殊福利的供应而言,这种做法并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被维护在相同的水平上)。
哪种决策属于这种类型,这是一个代表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即代表什么时候应该充当“受托人”(trustees)而行使他们自己的最佳判断,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充当表达选民意见的“委托人”(delegates)。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当前的观点仅仅是,在那些立法者应该充当“委托人”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总是无视某些公民的偏好,那么这种做法就应当引起反对,正如我刚才提及的其他情况一样。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公职人员都没有回应那些他们应该回应的理由。例如,在当前的情况下,公职人员就没有对由选民的观点或偏好所提供的理由做出回应。这种批评主要依据的是立法者对相关理由的回应,而不是选民影响他们的能力。
然而,公民应当能够利用投票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以免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忽视。 [16] 众所周知,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之所以失去共和党的连任市长提名,主要是因为在1969年冬季的暴风雪过后,皇后区的居民对于政府没有充分地清除积雪而感到愤怒。林赛最后作为无党派人士勉强获得了连任,但这个教训无疑对他的继任者和其他地方的市长的想法都产生了影响。
如果某个公民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少的机会来影响政治的结果,那么这将使他们面临着风险,因为他们更难采取上述方式来保护自己。但皇后区的居民所行使的影响力是否合法或者是否过度,这个问题取决于他们利用选举的权力所要求的是公平的待遇还是特殊的待遇,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影响力与其他行政区的居民所拥有的影响力的比较(如果其他行政区的居民选择行使这种影响力的话)。人们可能希望,如果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产生政治影响,那么他们对于影响结果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就会达到平衡的状况,从而产生公平的结果。但这不一定是真的。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影响政治的结果,这一事实并不能够保证每个人所经受的对待方式都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或违反某些特定的义务,例如确保每个人能够接受适当教育的义务。
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学校经费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用来说明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和堪萨斯州近期的立法机构都拒绝投票支持为贫困学区提供经费,从而使得这些学区达不到宪法规定的教育水平。这些情况都涉及我刚才所讨论的那类程序性错误,即未能履行提供适当教育的义务(这项义务是非比较性的),以及未能遵守平等关切的规范。显而易见,这些情况也表明穷人无法利用政治权利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不正义的对待方式,而且他们长期以来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17] 穷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可能是由选举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例如政党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也可能是由新泽西州的州长行使单项否决权的权力过大造成的。 [18] 但在普遍反对加税的情况下,即使贫穷地区的居民并不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少的机会去影响他人,他们依然很有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免受这类不公平的对待方式。为了提供这种保护,我们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措施是把这种保护列入依靠司法审查的宪法要求之中,但新泽西州的情况表明这种策略的效果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也表明不平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干扰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即使它不会干扰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如果穷人对于某些重要的服务需要额外的公共供应,但大多数人却足够富裕而没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很难确保那种为所有人提供这些服务的政策会得到足够多的政治支持。因此,虽然缺乏平等的机会去影响他人会使得一个群体面临着遭受不公平对待的风险,但是支持拥有能力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对待的理由与支持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影响他人的理由却有着不同的依据。
我之前论证过,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依赖于公职人员遵守某些行为标准,例如平等关切的要求,并且这些标准超越了对选民的偏好的回应。某种政治影响力之所以应当引起反对,是因为它经常诱导公职人员违背这些标准,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影响力比其他人有机会行使的影响力更大。当前关于学校经费的观点也表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选民。我们有一些适用于公民的政府机关的标准(同样也包括平等的关切),除非公民按照这些标准来行使他们的职权,否则政治制度将无法恰当地进行运作。公民光有平等的选票,甚至拥有平等的机会去产生政治影响,这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我想更仔细地考察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到不同的公民对影响政治结果所拥有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公民对影响政治结果所拥有的杠杆手段,例如通过开展政治竞选或捐助其他候选人的竞选,而且需要考虑公民若想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杠杆手段,哪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罗尔斯所说的各种政治自由的“价值”。
就投票权而言,要表明某些背景条件是使该项权利具有充分价值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这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首先,我们需要为公民提供教育,以便使他们能够理解政治问题并清楚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甚至能够比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要求人们应当拥有足够好 的教育,而不是必须拥有平等的教育。所以,对此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不平等本身,而是来自贫困和免费公共教育的供应不足。不平等之所以是一种威胁,主要是因为,正如我在讨论新泽西州的学校经费时所提到的,比较富裕的社会成员不太愿意为全民的良好公共教育买单。
其次,投票权的价值取决于投票者能否获得必要的信息,以便就如何投票做出明智的决定。既然拥有选票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让投票者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做出判断,那么关于政府实际做了哪些事情以及不同政策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类信息对于投票权的价值来说就格外重要。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自己收集这类信息。所以,为了让公民能够获取这些信息,我们就需要某些机构(包括大学和智库等机构)来收集这些信息,并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自由的出版机构和其他公共媒体来传播这些信息。
因此,如果政府拥有广泛的法律权力来控制言论和出版的内容,那么选举权的价值就会受到威胁。 但即便法律权力没有限制信息的流动,如果唯一的报纸和广播公司,或者更普遍地说,广泛传播信息的唯一有效机构,都归政府所有或由政府控制,那么这项权利的价值也会受到威胁。政府持有所有权的媒体确实也有可能会以公开和公正的方式进行运作。多年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与任何私营媒体公司一样出色。不过这依赖于一个政府自我约束的传统以及一个强大的新闻专业精神的文化,但考虑到政府官员在保留权力和保护自己免受批评这些方面上所具有的利益,这种传统和文化都是靠不住的。因此,政府对通信手段拥有所有权是一个冒险的赌注。
由单独的私营个体或个体的联合企业来控制一个国家的通信手段也构成类似的威胁。同样,私营企业主也有可能会以公开和公正的方式来经营这些机构,从而很好地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但这不太可能是真的。私营企业主可能不会有稳定的动机来保护政府免受批评以及避免难堪。但单独或多个私营企业主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仍然具有一套独特的利益,他们完全有理由来保护这些利益。由于威胁的依据在于一些能动者控制了主要的通信机构,并且他们代表着一套独特的利益,所以即便这些机构由多个共享特定经济利益的企业主控制,这种威胁依然存在。只要这些企业主还在争夺市场份额,他们就有动机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但作为社会中最富裕阶层的成员,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这是经济不平等损害政治自由的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当前的情况下,损害的是选举权的价值。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的分配本身,而仅仅在于不平等的财富可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种转化是难以避免的。
为了决定如何投票,公民不仅需要获得信息,而且还需要了解其他潜在选民的意见和意图。了解别人的想法对于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为了制订计划,我们也需要协调自己和他人的行动。皇后区的居民对积雪没有得到充分的清除而感到不满,并且由于他们都是邻居,所以他们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团体。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有共同利益的公民需要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他们既需要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意图,也需要拥有协调他们的活动的途径,以及拥有就如何投票达成统一立场的途径。政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组织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因此,这些组织的存在以及那些使公民更容易形成这些组织的法律和其他条件都会增加选举权的价值,而那些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的法律和政策则损害了这种价值。
现在我开始讨论针对政治问题的发言权和竞选选举职位的权利,而发言权对于竞选权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这些权利的价值取决于公民是否有能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想法或参选资格引起广大受众的注意。我已经讨论过不平等可能会以这些方式来干扰这种能力:一是富人控制了主要的言论手段;二是穷人没有足够的钱去获取这些手段;三是富人的获取途径要比穷人多得多,以至于穷人的信息被“淹没”了,从而得不到有效的倾听。
有很多策略可以用来缓解不平等的这些影响,包括限制媒体公司的所有权规模以增加竞争,提供公共媒体以降低获取言论手段的成本,为政治竞选提供公共资金,以及限制富裕候选人可以投入的资金数量。我无法在此探究关于这个议题的大量实证文献,但我观察到,鉴于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缓解这些问题已被证明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19]
人们在言论手段的获取途径上的不平等不仅会威胁到发言权和竞选权的价值,而且也以类似的方式威胁到选举权的价值。如果只有富人才能有效地获取主要的公共言论手段,那么这意味着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都无法获得那些他们有理由想要的职务。但这一点也会给其他人带来不正当的影响。因为它会使得公共话语所传达的观点的范围缩小了,而这将导致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更差的境况中来决定应该支持哪些政策,从而损害了投票权对每个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因此,如果只是简单地分析政治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富人和穷人的偏好,并且把这些偏好视为既定的偏好,那么作为一种理解不平等可能对政治公平产生哪些影响的方式,这种分析就过于狭隘了。
这也说明了各种政治自由的“价值”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选举权的价值依赖于他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和其他人的意见,而这又依赖于新闻自由和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更确切地说,这不仅依赖于媒体和其他人拥有这些权利,并且他们拥有行使这些权利的手段,它还依赖于他们实际上确实行使了这些权利 。最后一点是任何制度都无法保障的,但制度能够使它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发生。因此,如果一些政策会促进或干扰组建政党以及组建其他促进政治参与的社团,那么这些政策在这方面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自由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以下这种做法便具有误导性:仅仅将焦点放在这些自由对于那些拥有它们的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并且把这种价值理解为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自由来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正如柏拉图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除非一个人处在良好的境况下来决定应当影响其他人去做什么,否则影响他人的能力就是毫无价值的。 [20]
我们不仅要考虑权利持有者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那些因行使这些权利而受到影响的人的利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并且这种重要性不仅适用于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而且也适用于对权利内容的恰当理解。例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限制了政府管制和控制言论的权力。这些限制具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它们是保护重要利益所必需的手段。因此,要决定某项被提议的管制是否会侵犯言论自由,我们就需要确定它是否涉及某种会对这些利益造成威胁的权力。相关的利益不仅包括潜在发言人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中所获得的利益,而且也包括潜在听众(尤其是选民)从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中所获得的利益。 [21] 例如,在公开会议上限制发言时间,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正当的理由,不仅是为了让其他人拥有充分的发言机会,而且也是为了让与会的每个人能听到广泛的意见。
总结: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论证过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经济机会平等。当人们通过竞选来获得优势职位和那些通往优势职位的教育机会时,不平等便可能会干扰这个竞选过程的公正性。例如,当富裕的家长对大学招生人员或者对公职人员的招聘过程施加影响,从而使其子女比其他更合格的申请人更受到青睐时,上述这种情况便会发生。而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无法进入学校,从而无法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竞争好的工作岗位或大学录取资格,那么经济不平等就会干扰实质机会。
在这一章中,我论证道,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类似的方式来干扰政治公平。它可能会干扰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正如当富裕的公民对立法者或其他公职人员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做出有利于富人利益的决策时,情况便是如此。经济不平等也可能会干扰到政治公平所要求的背景条件,例如贫穷的公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去获取有效的言论手段,因此不太可能在竞选公共职位时成为成功的候选人。政治公平的这两类失败都与影响力有关: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指的是富人对当选的公职人员所拥有的那种影响力;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缺乏平等的机会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以及影响更广泛的政治决策。
这个描述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已经论证过:在第一种情况下,当立法者和其他公职人员因受到影响而做出有利于富人利益的决策时,我们对这种行为的根本反驳是,这些决策违反了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标准。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那些违反程序公平的行为一样,影响力之所以相关,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违反行为会发生,而不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应当遭到反对。但富裕的公民之所以能够行使此类影响力,是因为政治公平所需求的背景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对主要言论手段的获取。经济不平等导致富人拥有并控制着主要的言论手段,或者导致对这些手段的获取变得非常昂贵。因此,富人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公众对政治问题的讨论。这不仅对其他希望影响政治结果的人构成了问题,而且它也是所有公民的问题,因为为了决定如何投票以及支持谁,所有公民都需要接触更广泛的意见。此外,由于展开一个成功的政治竞选如此昂贵,所以富人自己更有可能会当选,并且富人还会对其他候选人和公职人员产生影响,因为他们需要依赖富人的捐款。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可以用来阻止经济不平等产生这些后果。但经验表明,一旦高度的经济不平等被建立起来了,要阻止它产生这些后果就会非常棘手。
[1] Martin Gilen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and Affluencand Influenc , chapters 3 and 4.
[2] Larry Bartels,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后续的研究对吉伦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质疑。参见Peter K. Enns, “Relative Policy Support and Coincidental Representation”,以及Omar S.Bashir, “Testing Inferences about American Politics: A Review of the ‘Oligarchy’ Result”,至于吉伦斯的回应,参见“The Insufficiency of ‘Democracy by Coincidence’ : A Response to Peter K. Enns”。
[3] Justice as Fairness , 139.
[4] 杰拉德·高斯在回应罗尔斯的反驳时指出,美国的政治参与程度很高。参见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 515-20。
[5] Political Liberalism , 327.
[6] Justice as Fairness , 46.
[7] 对于另一种观点的辩护,参见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根据这种观点,政治职务应当依据个人的优点来挑选候选人。
[8] Cohen, “Money, Politics, Political Equality,” 273. 尼科·克洛德尼(Niko Kolodny)也强调了影响力的机会平等这种观念,参见“Rule Over None II: Social Equalit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Democracy”。克洛德尼主要讨论的是影响力的形式机会平等,人们通过投票来行使这种影响力。科恩和我则主要关注的是克洛德尼所说的“影响力的非形式机会”,他在论文的结尾讨论了这一点(332ff.)。
[9] 第五章中关于“意愿”的观点在这里也适用。在相关的意义上,一个人能够获取某种手段,这不仅要求他能够使用这种手段(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而且还要求他处在一个良好的境况中来决定是否要使用这种手段。
[10] 科恩写道:“在1996年,比对手投入更多资金的候选人赢得了92%的众议院席位和88%的参议院席位。”(“Money, Politics, Political Equality,”281.)正如他所指出的,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复杂的,因为在任者更有可能赢得选举,也更善于筹款。科恩总结道:“撇开复杂性不谈,看起来不可否认的是,候选人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在筹款上的成功,筹款能力则依赖于他们的表现,而要获得那些提供资金的群体的支持则依赖于他们的行为。通过提供这种支持,捐款人会对选举的结果拥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第283页)
[11] 因此,正如在机会平等的“实质机会”成分的情况下一样,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程序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从而也是比较性的,所以这会推动一种充分的“充足”概念(an adequate conception of “sufficiency”)迈向平等。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如果大学录取和其他选拔机制确实在程序上是公平的,那么这种影响即便没有被消除,也会受到限制。类似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会减少政治竞选对资金的依赖。
[12] 有一些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选举事实上是由无关因素决定的。参见Christopher Achen and Larry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
[13] 吉伦斯从他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富人之所以对政治结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此的最佳解释是他们在竞选捐款上投入了更多的钱。参见Affluence and Influe , chapter 8。
[14] Gilen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781.
[15] Bartels,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263.
[16] 这就是贝茨(Beitz)所说的公民从公平的对待方式中所获得的利益。参见Political Equality ,esp. 110-13。在这里,政治公平和机会平等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一个人应当拥有某些手段,以便确保那些自己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制度是公平的,这种观念并不是经济机会平等的一部分。
[17] 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在1973年介入此事,想必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18] 在新泽西州的例子中,不公平划分选区的行为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00年人口普查后的立法重划选区比在此之前或之后的几十年都更有利于少数群体。(2001年,在重划选区委员会任职的拉里·巴特尔斯谈到已被通过的重划选区计划时,说:“我认为这将给新泽西人一个公平的机会去对立法者表达他们对立法者的看法。”参见Philadelphia Inquirer , Apr. 13, 2001。)这项计划生效后,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于2008年通过了首个学校资助法案,该法案由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批准,以便满足宪法的这个要求:只要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政府就必须为所有儿童提供“全面和有效”的学校教育。然而,由于2010年新一届州长的选举,这项法案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施。而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重划选区则再次削弱了贫困地区的权力。
[19] 问题的性质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也取决于相关的通信形式。我们很难说这两者会如何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改变。
[20] Plato, Gorgias , 463-9 et passim. 克洛德尼指出了这一点,参见“Rule Over None II,”310, 332。这可能也是罗尔斯为什么要强调基本自由的“最佳总体系”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参见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178-220。
[21] 在一些人看来,选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 Political Freedom 。我已经论证过,言论自由的内容取决于潜在参与者、受众成员和受言论影响的旁观者这三种人的利益,以及取决于在其他方面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参见我的“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ategories of Expression”。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针对追求平等的反驳,即促进平等会干涉个人的自由,并且这种干涉让人无法接受。例如,罗伯特·诺齐克便以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为例生动地提出了这种反驳;此外,哈耶克等人也都提出了这一点。 [1] 但一个用来支持更大程度的平等的论证也可以诉诸自由的价值。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反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理由是,它导致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因此,在关于平等的争论中,双方都可以诉诸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自由。我在本章的目标是,通过考察那些有争议的自由观念和我们在乎自由的各种理由来澄清这些争论。
干涉一个人的自由会导致他无法去做他可能想做的事情。所以,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对自由的干涉看起来就是他拥有初步的(prima facie)理由去反对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是下述这种想法背后的依据:如果一个行动干涉了某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必须为此提供特殊的证成,但没有干涉个人自由的行动则不要求提供这种证成。 [2] 例如,如果关于某项政策,我们只知道它干涉了某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来反对那项政策。因此,为了使这项政策获得证成,它的支持者就必须表明这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实际上并不适用,或者它被其他的考虑因素压倒了。
然而,这里并没有显示出自由的任何独特之处。因为同样正确的是:如果关于某项政策,我们只知道遵循这项政策会导致一些人变得非常贫穷,并且他们会比在其他可选的政策下要穷得多,那么我们显然也有理由来反对这项政策——这个理由也需要被表明是不适用的或者会被压倒。但即使这种对证成的需要并不是对自由的干涉所独有的,它似乎也表明,自由与平等之间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对比。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人们往往不清楚我们有哪些理由来关注平等本身(即关注一些人的拥有物和另一些人的拥有物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关注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东西。平等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模式(正如诺齐克对它的描述),或者只是人们出于嫉妒而关注的事情。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尽管不平等表面上看来并非总是应当受到反对,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不平等都有很好的理由,而我们需要探究这些不同的理由是什么。同样地,就自由而言,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会导致一个人无法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并且对这一事实的反对也存在着不同的理由。因此,要理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可能冲突,我们就需要理解在各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不同理由。
我之所以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某些人或机构所能够提供的,他们甚至可能积极地阻止我拥有这些资源。此外,我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也许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教育,并且我可能是因为负担不起学费才无法接受这种教育。同样地,我之所以无法到达我想去的地方,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汽车,也没有钱去购买或租用一辆汽车。
哈耶克会说,我在这类情况下并不缺乏自由(liberty),而只是缺乏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权力(power)。他认为,将自由等同于这类权力会忽视自由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会导致我的自由总是随着我的财富的增减而增减。哈耶克说,只有当别人通过身体的强迫(或强制)来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时,我的自由 才会受到干涉。他说,这一点会发生在以下这种情况之中:“某个人的环境或处境受到了另一个人的控制,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恶果,他被迫服务于另一个人的目的,从而不能按照他的连贯计划来采取行动。” [3]
自由与权力的这种区分对于哈耶克捍卫他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保障基本收入会让很多穷人增加他们的权力,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做他们有理由想做的事情。虽然这项政策需要通过税收来获得支持,并且这种税收干涉了自由,但如果增加穷人的权力可算作增加他们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的增加就需要与对自由的干涉相权衡,而且前者可能比后者更重要。可哈耶克会拒绝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虽然税收会干涉自由,但保障收入却不会增加自由,因为后者只是给予人们更多的权力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哈耶克正确地指出,许多强制的情况会具有某种独特的不正当之处,而且并非每次某个人由于缺乏手段而无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种不正当的特征都会直接呈现出来。例如,在刚才提到的那些例子中,我之所以无法接受教育或无法到达我想去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以处罚来威胁我,以便让我服从他的这个“计划”——让我别做这些特定的事情。
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之所以无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确实是由强制导致的。缺钱之所以导致我无法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是因为如果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必须拥有或使用别人的财产。而只有当我拿钱和别人交换时,他才会允许我拥有或使用他的财产。我不能简单地把某辆车开走,因为周围所有的汽车都属于某些人的财产。法律禁止我在未经物主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汽车,否则我将受到惩罚。因此,我之所以无法在缺钱的情况下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由财产权导致的,并且这种财产权受到强制的支持,而且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都为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在我获得我想要的东西的权力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那些情况下。
罗伯特·黑尔(Robert Hale)很久之前就强调过这种“背景强制”(background coercion)的重要性。 [4] 但黑尔接着提出了一个不太可信的主张。他说,如果协议的一方之所以同意某些条款,只是由于另一方的坚持使得他不得不同意,那么第一方的同意就是被强迫的。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如果我拿出原本用来购买食物的钱,去租用一辆我参加工作面试需要用到的汽车,那么黑尔会说,我是被迫支付这笔钱的。他很快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租赁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也不意味着我和他们签订的合同由于不是自愿的,所以是无效的。黑尔说,某件事情是否涉及这种意义上的强迫与它是否是错误的,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这样一来,每一种互惠互利的等价 (quidpro quo)交换就都是强制性的交换,而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对习惯用语的滥用,它甚至可能破坏了强制这一观念所具有的大部分力量。 [5]
然而,哈耶克关于自由和权力的区分所引人注目之处,并不在于他区分了强制和其他导致某个人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方式,而在于他区分了两种理由来反对某些因素阻碍某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管这些因素属不属于强制。一方面,我们有理由反对某些因素导致我们珍视的某个选项变得不可获取,或者我们只能以更高的代价或风险来获得它。这个理由的强度仅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强的理由想要获得那个选项。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种独立的理由来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并且不得不以哈耶克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来服从他的意愿。 [6] 支持这个反驳的理由具有多样性,并且这些理由不仅取决于那些更难获取的选项所具有的价值,也取决于其他的因素——在此我将提及其中的三种因素。
第一,反对服从另一个人的意愿的理由取决于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比起受到陌生人或长期对手的控制,受到家人或爱人的控制所引起的反对程度可能会更小(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
第二,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的理由取决于这个人有多大的自主决定权来决定你的行动。正如哈耶克所注意到的,当强制是由法律来规定时,它引起的反对程度会更小。 [7]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法律导致干涉变得更加可预测,从而允许人们在制订计划时能够把干涉纳入考虑之中。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种个人的因素:如果某个人能够命令另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比下述这种不同的关系遭到更强烈的反对,即某个人只能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理由来命令另一个人,并且这些法律既不是由他选择的,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某个人以一种格外不正当的方式依赖于另一个人的意愿。
第三,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控制会引起多大程度的反对也取决于我们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如何度过自己的私人生活(例如要和谁结婚)受制于某个人的命令,那么这要比某个人对我们的行为施加其他限制更糟糕(例如限制我们在盖房子时与我们的地产边界线保持多近的距离)。支持这一点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个人的选择是由别人决定的或者强烈地受到别人的影响(无论别人是通过威胁还是通过提供诸如金钱或工作等物品来施加这种影响),那么许多个人选择(例如配偶的选择)的意义就会被改变,而且通常都会遭到破坏。重要的是,某些选择应当只取决于我们自身所持有的理由,并且仅仅取决于某类特定的理由(例如经济收益以外的理由)。
因此,哈耶克所做的区分要比以下这个区分更加深入,即区分强制和以其他方式来限制一个人获得他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一点可以由下述这个事实展现出来:为了理解强制有哪些应被反对的地方以及为了决定强制何时可以得到证成,我们需要考虑我正在区分的这两类反驳。
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制会同时遭到这两类反驳。它通常包含着某种威胁——“除非你做A,否则我就会做B”;在此,B是受到威胁的那个人有很好的理由想要避免的东西。因此,这个人就有了我所提及的第一种理由来反对威胁,因为这种威胁导致他无法选择在不遭受惩罚的情况下不去做A,从而使得他的选择处境变得更差。此外,这种威胁之所以应被反对,也可能是因为服从这种威胁意味着一个人要处在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提供东西给别人通常不会被视为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做法会改善一个人的选择处境,所以不会遭到第一类反驳。
但提供东西给别人可能会以第二种方式而遭到反对。假设你的一个有钱的叔叔跟你说,如果你放弃立刻结婚的计划,他就会给你买一辆车。现在,你仍然可以选择不拿他的车然后立刻去结婚,并且你还有一个新的附加选项,即选择拿他的车然后迟一点再结婚。所以,看起来你的一系列选项并没有因为你叔叔的提议而变得更糟,甚至可能还有所改善。(尽管立刻结婚这件事对你的生活意义而言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它现在涉及放弃得到一辆你可能需要的汽车的机会。)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看起来像是一种强制,是因为你的叔叔试图控制你关于是否立刻结婚的决定。但这种决定是你有格外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由你自己来做出的决定,亦即想要独立于其他人的控制或影响。
强制性的威胁(或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提议)是否可被允许,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至少包括:(1)那个被阻止、变得更难获取或变得更缺乏吸引力的选项具有多大的价值,以及一个人对于参与这个选项所具有的资格;(2)如果一个人不服从这个已被提出的要求,会有多大的损失;(3)威胁者在剥夺你的这个选项时所具有的资格(姑且不论强制);以及(4)服从这个要求涉及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受到另一个人的控制。
让我们先考虑一下这个典型的例子:某个抢劫犯拿着枪对着你说:“要钱还是要命!”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有理由想要保住你自己的钱,也有理由想要活下去。此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它独立于任何与强制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你有资格保留你的钱,而且强盗没有权利杀你。在我看来,这一点就足以使得抢劫犯的这种行为不被允许(impermissible)。但除此之外,你还会有别的理由来反对受到抢劫犯的控制,因为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要求会让人感到羞辱。这类理由在其他情况下甚至会更加重要。
例如,考虑以下这种情况:某个雇主在经济上有很好的理由来减少他的劳动力,于是他对他的一个员工说,除非她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否则他会解雇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员工并没有资格要求继续工作,而且雇主有权利可以解雇她(这里姑且不论强制是否可被允许,因为它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雇主的这种行为之所以不被允许,是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以一种格外不正当的方式来利用这种解雇员工的权利去迫使员工服从他的计划;而这种方式之所以格外不正当,是因为它所涉及的那种选择具有个人重要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基于经济效率的理由(也许还有其他理由),雇主必须拥有权利来决定雇用哪个员工以及解雇哪个员工,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以上述这种方式来使用这种权力(就此而言,我们也不允许他们使用这种权力向员工或潜在员工索取礼物或其他好处)。
现在考虑一下刑法所涉及的强制。刑法会引起证成的问题,因为它所施加的惩罚涉及极其严重的损失,例如监禁、失去财产,甚至可能是失去生命;而人们通常有资格要求避免遭受这些损失。尽管如此,许多刑法看起来明确地获得了证成,因为这些法律为每个人提供了保护,也因为那些被制裁的特定行为是人们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去参与的行为,例如谋杀和持械抢劫。受制于这样的法律涉及被其他人控制,这个事实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当人们针对法律——例如针对环境法、分区法规、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例,以及更新近的税法——提出反对意见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基于那些被阻止的机会所具有的价值,而不是基于遵守这些法律涉及被其他能动者控制。当法律管制更私人的行为时,例如那些禁止吸毒的法律或要求摩托车手戴头盔的法律,后一类反对意见会变得最明显。在此,除了机会的损失之外,我们对由别人来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件事也会有合理的不满。即便我们不重视相关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永远都不会想到要不戴头盔去骑摩托车),我们可能也有理由感到不满。
从广义上来说,只要一个行动或政策对某个行动的过程添加了一个别人不想要的结果,并以此来阻止别人采取这个行动,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而任何广义上的强制性的行动或政策可能都会遭到我正在讨论的这两类初步的反驳。因此,要决定这种强制性的行动或政策是否可被允许,我们既需要考虑人们想要避免服从这种要求的这两类理由,也需要考虑允许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些理由。我现在的观点是,我们有多种多样的理由来反对广义上的强制性要求,这既包括那些想要获得某些机会的理由(即想要获得哈耶克所说的权力),也包括那些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的理由。
有了这些关于自由和强制的想法作为背景,现在让我开始谈一谈关于自由和促进平等之间的冲突问题。促进平等的一种方式是实施再分配的税收,这种税收从一些人那里取走资源,以便为其他人提供福利。而另一种促进平等或避免不平等的方式则是实施所谓的预分配 (predistribution),即实施某些法律和政策来决定人们的税前收入。 [8] 例如,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会造成税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被认为主要适用于这些方面。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迪士尼公司和默克公司所持有的专利权和版权的时间没有像现在这么久,那么这些公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富有。可以说,知识产权的范围越窄,不平等的程度就会越小。基于我即将讨论的理由,预分配会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但由于再分配的税收备受关注,所以我将首先对它进行考察。
税收似乎是一个干涉自由的典型例子。如果一个人不把一部分收入上缴为税款就会被罚款或受到监禁,那么他就更难以用必须缴纳的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此外,税收往往涉及一个人被迫为其他人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例如为自己不赞成的战争买单,或者为自己认为不应得某些福利的人提供福利,以及为自己认为是浪费金钱的体育馆或博物馆等项目买单。当法律要求某个人去偿还他欠下的租金或其他债务时,这一要求并不会以上述这种方式遭到反对,只要这些债务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自愿承担的,而不是由别人的意愿强加在他身上。
也许有人会回应,只要这些税款是由一个合法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所征收的,并且这一秩序已经批准了这些税款用于支付的那些费用,那么我们就仍然欠下这些税款。因此,在纳税中必须上缴的那些钱,就像欠下租金的那些钱一样,并不是一个人有资格保留并随意支配的钱。但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回应乞题(question-begging)了,因为它假定了税法的合法性,而这是我们正在争论的观点。然而,声称一个人有资格获得他的税前收入同样也预设了某个特定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具有合法性,人们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来赚取他们的税前收入。而税法正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它与这个框架的其他法律(包括界定财产权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依据。因此,以下这种主张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税收剥夺了某个人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根据这个法律框架 应当归他所有,所以税收是非法的。 [9]
由此可见,要理解对再分配的税收的反驳,最佳的方式并不是把它理解为:因为再分配的税收剥夺了人们的一部分税前收入,而这些收入是人们已经挣来的收入,并且根据他们置身其中的那些特定的法律制度,他们有资格获得这些收入,所以再分配的税收是不正当的。恰恰相反,对再分配的税收的反驳应当被理解为:如果某个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许再分配的税收,那么这个制度因此就是不正义的。(并且人们在此制度之内所赚取的税前收入也因此在道德上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污染)。 [10]
然而,任何合理的观点都会允许某些 形式的税收。例如,假设在一些人看来,为执法和国防所缴纳的税款是合法的,而且只有这些税款才是合法的。那么按照这种观点,尽管法律要求人们支付这些税款(否则他们就会受到罚款或监禁等法律处罚),但这些法律不会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不正当干涉。这些法律会是强制性的,并且通过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它们也以某种方式减少了人们可用来追求目标的手段;不过这些税收使得某些保护成为可能,所以它们也以其他方式增加了人们可用来追求目标的手段。
人们在这个制度下用来纳税的钱,就像他们用来支付房租的钱一样,必须是他们 自己的钱;也就是说,别人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拿走这些钱是错误的。但这种税收“拿走”了人们在这个意义上所拥有的钱,这并不构成对这种税收的初步反驳(即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反驳),因为人们没有资格保留这笔钱。然而,这不是因为他们保留这笔钱的权利被其他考虑因素压倒 了。我们保留支付房租的那笔钱的权利也没有被房东的要求所压倒。恰恰相反,我们并不拥有这种权利,因为我们已经签订了租约,或者在税收的例子中,因为我们是(有效的)税法的适用对象。
对这个案例进行归纳总结,我得出的结论是:执行税法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一个人欠下了某个东西,那么要求他偿还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对他的自由或财产权的不正当干涉。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合法地认为人们欠下哪些税款。这个关于一般的税收合法性的问题是我之前所说的预分配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于整体框架的合法性问题,而人们在此框架之内获得财产并交换财产以及赚取收入。举例来说,问题可能是:如果某个制度只允许一个人保留他从某些交易中所获得的一部分东西,那么这个制度是否可被证成?或者说,一个可被证成的制度是否必须允许这种交易的一方能够保留另一方所提供的全部东西? [11]
要确定某个制度框架所包含的税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我们既需要考虑为制定这些法律所提供的证成,也需要考虑针对它们的反驳以及它们被认为可能受到的限制。
以下是税法可能采取的三种证成形式。第一,对税法的证成可能基于下述这个理由:政治制度是一种做出集体决策以便执行计划的合法方式,这些税法则是一种为实施这些计划而筹集所需资金的公平方式。虽然我认为税法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但我不会在这里探究这类证成形式,因为它不仅需要捍卫一种政治合法性的一般理论,而且它也不太可能诉诸平等的考量。
税收的第二种证成形式则认为,为了让法律和政治制度本身(包括它所包含的财产法)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必须提供某些福利,而征税则是一种为这些福利买单的公平方式。例如,这些福利可能包括教育和其他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经济所必需的条件,以及那些为了让他们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所必需的条件。第三种证成形式则主张,征税只是为了减少不平等,因为不平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或者因为不平等会带来有害的后果,例如导致政治制度的腐败。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特别是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过第二种类型的论证。出于讨论的目的,我在这里把它们罗列出来,并且接下来还会提及某个更深入的论证。但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另一方的论证。而另一方所提出的一个论证是,因为税收与人们所拥有的独立于任何社会制度的财产权是不相容的,所以它是不正当的。这并不是目前最普遍的观点。 [12] 但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它会具有吸引力。
这个观点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认为那些界定财产权的社会制度有可能会遭到道德批评。换言之,不是任何界定这些权利的方式都是合法的。这种批评看起来必须以人们拥有某些独立于此类制度的权利作为依据,而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备选答案。另一个更具体的支持理由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一些明显错误的行为,它们完全独立于任何社会制度,并且它们看起来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们涉及侵犯财产权。
假设某个家庭清理了一些土地,之后种上了庄稼以维持冬天的生存,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错误地对待任何人——用洛克的话来说,他们给其他人留下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如果一群武装人员随后走过来取走这些庄稼,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用契约论的术语来说,任何允许这种行为的原则都是一种可以被合理地拒绝的原则。
拒绝这样一个原则的理由是,如果人们处在那个家庭的位置之上,那么他们必须能够养活自己,并且能够对将来使用某些物品拥有足够的信心,以便使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制造这些物品对于他们而言会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这些理由足以拒绝一个允许取走这些庄稼的原则,因为这里并不存在着同等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应当允许取走这些庄稼。由于那个家庭的行为已经给其他人留下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所以其他人有机会采取与那个家庭相同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我们既有理由想要控制那些用来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也有理由想要稳定而持续地控制这些财产——这是我们要制订和实施自己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这些理由都是拒绝上述那个原则的理由,并且它们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也是使得个人财产权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13] 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设想的那个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它侵犯了那个家庭的财产权。但这是一种误解。侵犯财产权的错误在若干方面上都不同于干涉某些利益的“自然的”错误(“natural” wrongfulness),即便正是那些利益使得财产变得重要。
我所描述的那种明显的自然的错误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作恶者显然已经干涉受害人,并且是在他们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清楚哪些行为构成了干涉。如果我在你的土地下面挖隧道来开采矿床,但你却不知道那里有矿床,那么我有没有干涉你呢?或者说,如果我在我们的财产分界线附近挖一口井来开采石油,但大部分石油都位于你的土地之下,那么我有没有干涉你呢?财产的社会制度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界定人们对土地的控制权和对其他服务于我所列出的基本财产利益的物品的控制权。如果既定的制度以一种可辩护的方式界定了这些控制权,那么侵犯它们所界定的权利就是错误的,无论某种特定的侵犯实际上是否涉及对受害人的生活和活动的干涉——在干涉被理解为独立于这种制度的意义上。而且不管能动者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是否拥有某些提供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的替代方案,这种侵犯都可能是错误的。
由制度界定的财产权还包括转让权,即授予他人对某个物品的排他(exclusive)使用权,而这种权利并不取决于第三方对该物品的使用是否会在一种独立于这种制度的意义上干涉受让方对该物品的使用。此外,受让方所获得的排他使用权也不取决于那些被禁止使用该物品的人是否能够拥有“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转让本身就授予了一种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允许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想要获得那个被转让的物品的主要理由,仅仅是为了拥有权力来禁止其他人使用它,以便要求其他人为使用它而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人们可以把该物品保留到之后的某个时期,在此时期,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不足导致该物品的价格上涨。为了以后的交换而保留某个物品,这是对这个物品的一种使用方式,但这种使用方式本身就依赖于一种禁止别人使用它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受到这种权力的保护)。
这并不是说,这类权利无法得到证成;而只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类免于干涉(non-interference)的论证来证成这类权利。尽管人们需要保护这些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但除了基于这个需求以外,制度所制定的财产权还可以基于其他工具性理由来获得证成。这种证成必须考虑在特定情况下建立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包括它的分配效果。知识产权就是这类权利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们是通过习俗或立法来制定的,并且可以用来转让和交换。
如果人们用“财产权”来指代这样一些权利——它们以上述方式超越了免于干涉的要求,并且这些权利的持有者还有权力将它们转让给其他人,那么所有财产权都会以这两种方式依赖于社会制度:第一,它们是由社会制度来界定的;第二,对它们的证成依赖于对这些制度的证成。因此,不存在自然的财产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无论制度以哪种方式来塑造和修改财产权,都不会遭到道德批评。 [14] 制度能够界定财产权的方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权利必须以某种方式去促进和保护重要利益,或者更广泛地说,必须与重要利益相容,否则它们将无法获得证成。这些重要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我所说的我们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而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这种利益能够成为那些独立于任何制度的错误行为的依据。
当一种特定的产权制度采取了我所描述的那种充分扩展的形式时,这种制度是否可被证成,以及侵犯它所界定的权利是否因此是错误的,就取决于这种制度所创造的占有制度和交易制度(system of holdings and exchange)的效果。如果这种制度所提供的好处足够重要,从而使得人们无法合理地反对这种制度禁止他们去使用他们有理由想要的物品和其他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能够获得证成。 [15] 自由的考量(包括但不限于人们有理由来反对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和经济效率的考量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挥着某种作用。只要我们有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基于不平等的后果或其他理由),那么这些理由也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权利体系的证成性取决于所有这些理由如何达到平衡。
一些例子可用来说明这个证成的过程。首先考虑个人财产的占有权和交易权的情况。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使用我们的生活空间以及使用那些执行我们的生活计划所需的物品,并且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禁止其他人使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需要指望我们在以后也能够使用那些执行我们的计划所需的物品,所以我们有理由禁止其他人使用它们。而如果界定或重新界定财产权的方式与这些最基本的理由不相容,那么它们就会在道德上遭到强烈的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我可能拥有的任何计划而言,如果一个法律制度没有为我提供对执行该计划所需的物品的控制权,那么它就会遭到反对。因为其他人也有理由去执行他们的 计划,而给予我这种控制权可能会与他们所拥有的理由不相容。 [16]
这意味着,一种可辩护的产权制度在界定那些权利时需要对每个人 所拥有的这类理由做出回应。通常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回应其中的某些理由时,有些方式可能没有涉及财产权。例如,我们有理由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空间,而这些理由也许可以由某种租赁制度来做出回应,即便这种租赁制度不像财产权那样把出售的权力也包含在内。然而,无论是由法律制度还是由习俗在起到保护这些利益的作用,只要某种改变会导致它们无法继续保护这些利益,那么这种改变就会遭受到强烈的反对。即便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会促进经济平等,它也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17]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极端来考虑法律创造知识产权的证成过程。专利法和版权法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例如禁止制造和销售某些药物,或者禁止复制某些文本和图像。因此,通过使人们受制于某些以惩罚作为威胁的命令(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降低了他们的自由),这些法律会导致人们更难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此外,由于一些人想要服用这些药物或欣赏这些图像,但这些法律却导致这些东西变得更加昂贵,因此它们也降低了这些人的权力。
另一方面,这些禁止他人使用某些物品的权利会为专利和版权的持有者提供收入,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扩大这些权利的范围,例如延长专利和版权的有效期,或者使它们适用于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将使这些权利的持有者变得更加富有,从而更容易获取他们想要的物品。因此,这种做法可能会鼓励其他人来发明这些东西。
但这种做法也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所以,如果 我们有理由来避免或减少这种不平等(也许是基于不平等的影响),那么这些理由就会支持缩小这些权利的范围。据我所知,缩小知识产权的范围并不会遭到基于减少自由的反驳,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考量作为依据。范围更窄的权利会降低权利持有者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但却会增加其他人相对应的能力。此外,在这两种安排下,国家对人们的支配程度看起来是一样的。
总之,即便撇开平等的问题不谈,对自由的考量也会要求 缩小这些权利的范围。至少它们不会反对这么做。支持延长专利和版权的有效期的主要理由是,我们需要用它们来激励人们生产有用的产品。因此,如果这里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那么这种冲突是:这种方式(即增加一些人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权力”)所能够提供的效益和那些有利于平等的考量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对证成过程的这种描述通常能够应用到这个问题之中,即对财产权的界定应当受到哪些道德限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证成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看起来清楚的是,平等的考量会起到某种 作用,而且它们并不因为有时候会与自由的考量相冲突就被排除掉。自由与平等之间发生最直接的冲突是在这些情况下:不平等是由特定的交易产生的,并且人们在这些交易中行使了他们显然必须拥有的那些权利。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通过限制这些交易或者对由这些交易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我们才能促进平等。
诺齐克关于威尔特·张伯伦的例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威尔特从他的粉丝那里获得了额外的美元,因为他们喜欢观看威尔特的比赛,而这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严重加剧。即便我们有理由来阻止这种不平等,但我们却不能通过禁止威尔特和他的粉丝的行为来阻止它。如果一个人想要把钱花在篮球比赛的门票上,但是他却不能这么做,那么钱还有什么用呢?此外,是否要为一定数额的金钱去参加比赛,这必须取决于威尔特的意愿。所以看起来要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威尔特的收入进行征税。那么,由哪些因素来决定这种做法是否可被允许呢?这个问题是以下这个更普遍的问题的特殊情况,即人们是否能够要求保留通过各种交易所获得的全部金额。接下来我会先考虑由交换财产来获取利润的情况,然后再回到为服务付费的情况。
让我们以通过出售房屋来获取利润作为例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成财产权的个人理由会显得特别强有力。毕竟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控制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想要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以及随心所欲地禁止别人使用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人们关心财产的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此外,人们也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选择居住地,以及随心所欲地改变居住地。基于这些理由,一个可辩护的权利体系必须规定人们能够禁止别人使用他们的个人空间,并且不得要求他们居住在某些地方或禁止他们随心所欲地搬迁。
但现实的情况仍然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住在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因此,一个允许房屋在市场上转让的房产制度便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这种制度使得人们能够稳定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空间,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搬迁,除非别人给他们提供的价格使得搬迁对他们来说是可取的[即提供某些至少符合他们的“保留价格”(reserve price)的东西]。将稀缺的住房分配给那些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的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导致资源的分配能够回应人们对住房的不同品位,以及能够回应住房(与其他商品相比)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至少当金钱的边际效用对不同的人而言大致相同时,它会具有这种效果。而当财富和收入极其不平等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可交换的住房产权,并且这些理由部分依赖于那些支持人们关心财产的最基本的个人理由,以及部分依赖于刚刚提到的那种效率的考量。对于后者,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制度有助于确保适当数量的住房,因为如果住房的数量稀缺,那么房价的上涨会吸引更多的住房建设投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考量所支持的住房产权是否会阻止对转售房屋所得的利润进行征税。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阻止这一点,尽管它们对这种税收施加了限制。首先,买方和卖方必须事先知道他们将会付出什么和得到什么。(合理的期望应当受到保护。)其次,卖方至少要得到他们的保留价格,而且买方不能被强迫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至于超过房产对于他们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再次,市场的效率属性依赖于这种情况,即如果某些潜在买家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卖家把房产卖给这些买家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即便是税后的收入。因此,税收不能取走卖家超过其保留价格的所有收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卖家保留买家所支付的全部金额。
买家愿意支付多少费用,这当然取决于买家拥有多少钱,但同时也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获得其他同样理想的房子。所以,我刚刚得出的结论是,支持住房产权的那些理由并不会支持这个结论——卖家有资格得到其财产的全部稀缺性溢价(scarcity premium)。用诺齐克的话来说,任何这样的税收都会干涉某些“成年人之间自愿同意的资本主义行为”,因为它们会阻止卖家在交易中能够精确地保留买方所支付的费用。然而,虽然买卖双方能够精确地进行这种交易会给卖家带来某些利益,但这些利益比起我已经提到的其他产权利益而言看起来却相当薄弱。
这也许让人感到不太满意。如果我们对现实中的房地产交易进行征税,可收益却直接进入总统的个人银行账户,那么即便这项税收遵守了上述的限制,它也会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即便这项税收在交易之前已广为人知,而且我认为即便相关的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它也会遭到反对。而要解释为什么这项税收会遭到反对,我们能否不诉诸这种观念,即卖家的财产权使得他们有资格得到其他人为获取卖家的财产所愿意支付的全部金额?(或者说,我们能否不诉诸这种看起来更不可信的观念,即买家有资格不去支付超过卖家实际所得的费用?)
这类税收之所以会遭到反对,首先是因为卖家有理由想要保留更多买家自愿支付给他们的金额,所以如果卖家没得到这种金额,那么我们必须给出某些理由来支持这一点。其次,没有任何好的理由会支持为了让总统以这种方式从每笔交易中获益,卖家应当得到更少的金额或者买家应当支付更多的费用。因此,如果对交易的利润进行征税是正义的,那么这一定是因为,除了这些税收事先已广为人知以及它们是由公平的程序所制定的,我们还拥有好的理由来支持这些税收。
我正在考虑的这两类理由都来自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合法性所要求的条件,并且它们也是支持促进重要公共物品的理由。但我将集中讨论前一种理由,既因为它们所支持的税收最有可能是再分配的税收,也因为这是平等的考量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为了使我刚才所描述的产权制度能够回应每个人在住房上的基本个人理由,住房市场就绝不能导致最贫穷的社会成员根本无力负担起住房的费用。因此,为了让整个产权制度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公共住房,或者更普遍地保障最低的基本收入。
通过投资住房来获取利润,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会产生我在其他章节讨论过的那些消极后果,那么对由出售财产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可能就是控制这些消极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最佳方式。只要我们在我所描述的范围内这么做,那么这种做法就会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它们既不会干涉人们在想要选择和控制自己的住房这方面所拥有的重要理由,也不会干涉为那些最愿意支付住房费用的人分配住房的效率。我在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要描述或评估所有这些理由。倒不如说,这里的要点是,支持住房产权的这些理由原则上都不反对我们对交易的利润进行征税。
现在我开始讨论对人们的工作收入进行征税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从“自由选择职业”的重要性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每个人都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选择如何使用他的生产力。这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来拒绝那些允许人们被迫从事某一特定工作的法律或政策,并且每个人应当能够按照他的选择而自由地辞职。但是,“被迫”和“自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通过立法来要求人们从事某些工作,这会是不可接受的(也许像征兵这样的紧急情况是例外)。不过人们也有理由想要处在良好的条件下来选择职业。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我在第五章中讨论了这些理由——想要了解他们可能会从事的各种工作,并且想要能够获得资格去从事那些适合他们的工作。
另一方面,就像住房一样,人们不可能总是准确地拥有他们想要的工作。而就业市场会允许人们在某种工资的背景下来选择工作,并且这种工资背景反映了人们的选择给其他人所带来的成本。没有人必须为某种低于他的保留工资的薪水而工作(考虑到其他的替代方案),雇主也不必支付更多的工资,以至于超过工人对于雇主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在这样的制度中,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会被有效地分配到工作岗位上(也就是说,这种分配方式能够回应对这些技能的需求)。此外,这种制度还具有灵活性:随着需求和技术的改变,劳动力将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被转移到不同的用途之上。
虽然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效率优势,但这些考量并不反对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收入进行征税。除了我已经提及的那些要求,“自由选择职业”还要求人们应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从事第二份工作,以便赚取更多的收入。 [18] 而如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于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取走人们所能够赚取的、超过一定数量的全部额外收入,那么这种做法将无法得到证成,因为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根据他们在工作、休闲和其他消费形式之间的不同偏好来采取行动。
然而,有人可能会论证:如果一个实体有权力对其他人自愿为某个人的劳动所支付的部分费用进行征税,那么该实体就会是这个人的劳动的部分所有者;并且这种做法将类似于奴隶制,因为它与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在此,自我所有权的观念指的是,人们是他们的精力和才能的唯一所有者,并且对如何使用这些精力和才能拥有唯一的自主决定权。 [19] 要评估这一论证,我们就需要追问:自我所有权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以及其吸引力背后的理由是否会支持人们有资格获得其他人自愿为其服务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在这里,我只是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自我所有权而已——我在这本书中一直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平等的观念,而在这一章中则把它应用到自由和强制的观念;也就是说,我试图确定这些观念基于哪些理由而具有重要性,并追问这些理由何时适用。
说我们是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的所有者,比如说我们是我们的眼睛和肾脏的所有者,这种说法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有人未经我们的同意就从我们身上取走这些东西,那么这会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是,我们也有权力把这些东西送给别人,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把它们卖掉。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我们的劳动的所有者,以及这一点对于税收的证成性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已经提到的这些考量充分地把握到了人们对其劳动拥有自我所有权这一观念所具有的合理之处: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他们的职业,以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辞职,等等。这些理由解释了为什么诸如奴隶制等否定自由选择职业的制度是不合法的。但这些考量并不意味着工人有资格得到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即雇主自愿支付的最高工资——这取决于对工人的服务的需求和他们所提供的技能的稀缺性。对人们的部分收入进行征税并没有被这些理由排除在外。所以,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来支持这种税收,那么进行这种征税就会是合法的。 [20]
正如我已经表明的,在这些理由之中,最核心的理由是:为了使财产和市场交易制度成为合法的制度——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来赚取他们的收入,我们需要提供这种合法性所要求的条件。我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些理由,包括那些由高度不平等的消极后果所提供的理由。基于这些理由对某个人征税并不能被恰当地描述成是在强迫这个人使用他的合法资源去帮助其他人。恰恰相反,这些税收反映了在一个合法的财产和市场交易制度下,这个人针对他能够拥有哪些资源所提出的要求会受到这些税收的限制。
在支持税收的那些理由中,有两个特定的理由会与我们当前关于自我所有权的讨论有关。市场经济的效率会要求雇主必须要有权力来向工人指派工作,并且有权力根据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来雇用或解雇工人。这些权力会让个体更难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和精力,也就是说会削弱个体在这方面上的能力。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工人都产生了影响,但对于那些拥有最低水平的市场技能的工人而言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必须在其他人的控制下去从事那些往往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工作,以便获取谋生之道。
所以,工人有理由来反对这些权力,并且他们所拥有的理由是那些位于自我所有权观念背后的基本理由。即便这些理由不足以构成完全拒绝这些权力的充分理由,但考虑到支持这些理由的那些论证,它们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要求我们在界定这些权力时,必须限制这些权力对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来实现,亦即确保人们能够发展更广泛的技能,从而能够采取更广泛的就业形式。它也可以通过这些策略来实现:一是采取某些措施以便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例如制定法律来提高工会的权力;二是向所有人提供最低的基本收入,从而确保即便是最不合格的工人也能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之上,由此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拒绝某些特定的工作形式。 [21] 这些策略的优点在于,它们让工人自己来决定是想要提高工资,还是想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对收入进行征税以便能够提供这些福利,这种做法会阻止人们获得其他人自愿为他们的工作所支付的全部金额。但是,当我们纯粹从支持自我所有权观念的那些理由——尤其是想要不受他人控制的理由——来看待这个问题时,人们所放弃的东西就远远不如获得这些福利的人所得到的收益那么重要,而正是税收使得这些收益成为可能。
将自我所有权理解为一种禁止受到侵犯的“边界约束”(sideconstraint)会阻碍这种比较。但是,为了决定是否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约束,我们需要审视这种约束背后的理由,正如我一直在做的那样。而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这种普遍形式的约束。
[1] Hayek, The Constitutions of Liberty , 87; and “Principles of a Liberal Social Order,”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171.
[2] 参见杰拉德·高斯的“基本自由原则”。该原则认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是道德的现状(status quo),即自由不要求提供证成,但对自由的限制则要求提供证成”(Gaus, Social Philosophy ,119)。此外,也可参见他对自由推定的讨论(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 340–8)。
[3]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20-1, 133.
[4] Hale, “Coerc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pposedly Non-coercive State.”G. A. 科恩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参见“Justice, Freedom, and Market Transactions”。对黑尔的观点的讨论,参见Barbara Fried, The Progressive Assault on Laissez Faire 。
[5] 尽管当我们仅仅以这种等价的方式来理解交换时,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太理想。对交换如何可能缺乏这种不正当的特征的调查,参见A. J. Julius’s “The Possibility of Exchange”。
[6] 这个理由一直被共和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家所强调。参见Philip Pettit’s Republicanism 和 Just Freedom ,以及Quentin Skinner’s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 chapter 2, esp. 84。
[7]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21. 佩迪特(Pettit)和斯金纳(Skinner)也强调,不自由的不正当之处在于它意味着服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意愿(Republicanism , 55-7;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 70)。
[8] 我从雅各布·哈克(Jacob S. Hacker)那里沿用了“预分配”这一术语,参见“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Middle-Class Democracy”。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在更早的时候使用过这个术语,参见“The Future of Money”。马丁·奥尼尔(Martin O’Neill)和萨德·威廉姆森(Thad Williamson)更广泛地讨论了这个概念,参见“The Promise of Predistribution”。
[9] 这就是墨菲(Murphy)和内格尔(Nagel)在《所有权的神话》(The myth of Ownership )中所提出的观点,他们对所谓的“日常的自由至上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参见The Myth of Ownership , esp. 31-8。
[10] 墨菲和内格尔讨论了这种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并把它与“日常的”自由至上主义进行对比,参见pp. 64-6。
[11] 这种方式也可以用来表述墨菲和内格尔的著作的一个主要观点。不过,《再分配和预分配》作为书名就不如《所有权的神话》(The Myth of Ownership )那么简洁有趣。
[12] 以下这些人都拒绝这种观点: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158-9;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26; 以及更近的Gaus, 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 509。持不同意见的人则包括Nozick和Eric Mack, “The Natural Right of Property”。
[13] 参见Freeman, “Capitalism in the Classical and High Liberal Traditions,” 31 and n. 27, 和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53, 54。
[14] 针对墨菲和内格尔的《所有权的神话》,一些批评者错误地把他们在书中捍卫的观点解读成蕴含着这一点。
[15] 当诺齐克意识到需要添加他的洛克式的限制性条款(Lockean Proviso)时,他也认可了这个一般性的观点。参见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175-82。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证成性的门槛非常低。
[16] 诺齐克关于选择结婚对象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Having a Say over What Affects You” in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268-71。他正确地指出,我们并不具有某种一般的权利来要求对那些影响我们的事情拥有发言权。但是,一些界定权利的方式仍然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某些特定的方式会剥夺一些人对生活的控制权。因此,诺齐克所回应的那种反驳并不需要被表述为他所表明的那类不可辩护的一般权利。
[17] 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所涵盖的那些个人权利会包括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而且即便为了促进他的“差别原则”的实现,“平等的基本自由”也不能被废除。参见Samuel Freeman, “Capitalism in the Classical and High Liberal Traditions,” 19 and 31-2。
[18] 正如安东尼·阿特金森所论证的,参见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 186, 210。
[19] 众所周知,诺齐克提出了这种关于奴隶制的主张,参见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169-72。而G. A.科恩则发展了自我所有权的观念并把它作为对诺齐克的立场的最佳解释。科恩论证道,自我所有权的观念确实排除了那些针对劳动收入的税收,不过他随后又驳斥了这种论点,即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我所有者(self-owners)。参见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 chapters 9 and 10。
[20] 在这里,我至少部分同意大卫·高蒂尔(David Gauthier)的观点,参见Morals by Agreement ,272-6。G. A.科恩对高蒂尔提出了反驳,他论证道,自我所有权与针对收入的税收是不相容的,因为“只有当人们有资格为与其他人交换所有物的交易设置条款时,他们才是其所有物的排他所有者”。(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 221.)如果“设置条款”不仅意味着“在交易中获得人们的合理预期收益”,而且还意味着“获得其他人自愿支付的全部东西”,那么这个观点确实会排除税收。然而,我已经指出,“自我所有权”的吸引力建立在某些理由之上,并且这些理由也解释了为什么奴隶制是错误的,但我所提及的这些理由并没有支持上述这个观点。
[21] 正如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所论证的,参见Real Freedom for All 。
对不平等的证成有时候会基于这个主张,即那些拥有更多利益的人应得(deserve)这些利益。例如,最近格里高利·曼昆为首席执行官(CEO)的高额薪酬提供了辩护,他的理由便是:首席执行官基于他们的生产力而应得这些报酬。 [1] 但另一方面,应得的观念也可能会被用来为相反的结论辩护。例如,有人可能会主张,即便高管的高额薪酬提供了某些提高生产力的激励,可这些报酬仍然是不正义的,因为没有人基于从事这些工作而应得那么多的报酬。尽管这两个论证关于正义的薪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它们都共享了这个假定:经济报酬的水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应得而恰当地获得了证成。
我将在本章中论证,我们应当拒绝这个假定。“应得”这个词语被用来提出许多不同种类的主张。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进行区分并仔细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当一个人确实应得(或不应得)某种经济报酬时,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某些更广泛的正义观念,而不是它本身依赖于某种应得的观念。在这些情况下,应得的观念无论是作为对更多的经济报酬的证成,还是作为对这些报酬的限制,都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为了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这个否定性的结论,首先我需要考察不同种类的应得主张。然后,我可以运用这种理解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应得看起来会与分配正义的问题相关,以及为什么这种明显的相关性是错误的。
人们有时候会在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应得”:在这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方式,这仅仅是说他应当以这种方式来被对待,或者说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他是正义的。我们应当以人们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所应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一点(在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应得,那么关于人们应得什么的主张就会对下述这个问题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为什么以正在被讨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人们是正义的。尽管我们说那种方式是人们应得的,但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却可能是基于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某种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观点,或者任何关于正义的要求的其他观点。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关于应得的主张就仅仅指的是,这种主张关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正义观念所提出来的要求。而为了提供某种独特的依据来支持或反对不平等,关于应得的主张就需要拥有某些更加具体的道德内容。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方式则指的是,这种对待方式是由某些制度规定的。例如,如果某个班级的既定评分政策要求任何平均考试成绩高于95%的学生获得A等级,那么平均成绩高于97%的学生就可以说应得一个A等级的成绩。这种主张正是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和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制度资格(institutional entitlement)主张。 [2]
但不是任何制度都能够在道德上产生有效的制度资格主张。例如,某所学校的校规可能会规定,在某个学期中取得最低平均成绩的学生必须在一个学期之内担任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的私人仆人。然而,那些取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学生却没有资格获得这项服务,因为一种要求某些学生成为别人的仆人的制度是无法得到证成的。因此,尽管制度资格的主张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的正确性却依赖于对相关制度的证成,并且这种证成不需要依赖于一种独立的应得观念。不过,也许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应得,并且制度可以依据它们给予人们在这种独立的意义上所应得的东西来获得证成。接下来我将考虑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意义。我目前的观点只是,这种非制度性的(non-institutional)应得必须与制度资格的观念有所不同。
另一个与制度资格密切相关并且在道德上很有分量的观念是:没有实现合法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s)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某个学生努力将平均考试成绩考到高于95%以期获得A等级,但尽管他的平均成绩高于96%,却依然没有获得A等级,那么他就有一种合理的抱怨。通过诉诸该学生由于期望得到这种奖励而已经做出了牺牲,这种抱怨所具有的力量看起来就超越了制度资格的观念。(因此,制度资格是一个比合法期望更广泛的概念,因为制度资格的主张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已经以某种方式依赖这种制度。)但是,如果某个要求所具有的力量是建立在合法期望的观念之上,那么这个要求的力量依然还是依赖于相关制度的证成性。例如,如果某个学生之所以努力学习以便考到班上最高的平均分数,是因为他期望在下学期中能够让排名最低的学生来做他的私人仆人,那么即便他没有获得这项服务,他也不具有我正在描述的那种有效的抱怨。他可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来反对在这种奖励的前景上受到了欺骗,但是却没有资格要求获得这种奖励,因为规定这种奖励的规则是无法得到证成的。
为了作为评估制度的独特依据,关于应得的主张需要与关于制度资格或合法期望的主张有所不同。它们必须是非制度性的 ,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不依赖于某些以其他方式获得证成的制度。
如果基于应得的证成要具有独特性,那么它们也需要区别于基于效果的证成——这种证成的依据在于以某种方式来对待某个人会带来好的效果。通过剥夺某个孩子的奖励来训导他——“因为这是他应得的”,这不同于基于以下这种理由来采取相同的行动:因为人们认为这将改善这个孩子的品格或者让他(或他的兄弟姐妹)以后有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因此,在我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曼昆区分了两种对高管薪酬的证成:基于应得的证成和效用主义的证成,后者依据的是这些报酬所提供的动机会带来好的效果。)基于应得的主张同样也在这个方面上不同于基于需求的主张。例如,有人也许会说,某个人应得帮助,因为他正在挨饿;或者说,他应得医疗服务,因为他生病了。但这些证成实际上诉诸的是,给人们提供这些形式的对待方式会带来好处。相比之下,高管基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应得更高的薪酬,这种主张并不依赖于他们会比其他人从那些额外的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因此,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应得的主张是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受到对待的主张,并且这些主张是非制度性的(即它们不依赖于某些制度规定了这种形式的对待方式),而且它们不是基于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某些人会给他们或其他人带来预期的好处。这些主张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应得主张 ”,它们声称,仅仅 依据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就足以使得某种形式的对待方式成为恰当的方式;在这里,作为限制条件的“仅仅”,它排除了我刚刚提及的那两类证成:一是诉诸制度的证成,二是证成的依据在于以正在被讨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人们会带来好的效果。这种缩小关注范围的做法并不是特设性的(ad hoc),而只是反映了如果诉诸应得的主张要提供一种独特的论证形式来支持或反对不平等的对待方式,那么这些主张需要具备什么特征。
我认为,这种纯粹的应得主张有时候是有效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表达赞扬、钦佩、感激、责备或谴责等方面的应得主张。例如,如果某个人之所以采取某种方式来行动,仅仅是因为他想要让我受益,并且他自己为此还付出了某些代价,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得我的感激态度成为一种恰当的态度。我对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可能会让那个帮助我的人感到高兴,也可能会鼓励他或其他人以后采取这种方式来行动。但并不是这些效果使得我的感激之情成为恰当的态度。仅仅凭借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反映出的态度,就足以要求某种感激之情。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或者已经取得了某些其他形式的优异成就,那么这就会使得认可和钦佩成为恰当的态度,以及使得对这些态度的表达成为恰当的行为。此外,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福祉完全漠不关心,或者有意要伤害他人并因此造成了伤害,那么这一事实就能够使得谴责性的态度以及中止友好的感受成为恰当的。 [3]
这些判断的恰当性依赖于关于那个人的某些事实与相关的反应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费尽心思地帮助我,那么这个事实便以这种方式与我对他的感激之情相联系,并且也与我在适当的情况下更愿意帮助他相联系。而如果某个人屡次背叛我的信任,那么这个事实与我的怨恨之情以及我以后更不愿意信任他也有联系。
如果我采取这些消极的反应态度,那么这会让这些态度所针对的人付出某种代价。因为他们有理由在乎我如何看待他们,而且我在态度上的改变,比如我更不愿意信任他们,也会剥夺掉他们有理由想要的机会。但是,只要这些针对某个人的修正态度是恰当的,那么他就不能合理地反对这些代价。没有人能够无条件地要求获得我们的好感,我们也只应当把信任给予那些本身值得信任的人。因此,尽管一个背叛别人的人会遭受这些损失,但他对此并不能提出任何道德上的抱怨。
虽然这些态度的改变是针对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所做出的回应,但并不是只有当这些特征处在那个人的控制之下时,这些态度的改变才是恰当的。 [4] 它们仅仅 依据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而成为恰当的。我不能被要求去信任某个已经背叛过我的人,不管他本来是否能够选择不去成为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关于自愿和控制的事实会与这个问题相关,即某个特定的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态度(如果确实反映了某种态度的话)。当我的朋友由于遭受折磨而透露了我私底下告诉他的一些事情时,这一事实比起下述事实而言无疑反映出了他不同的忠诚度,即假设他在闲聊中仅仅为了好玩就相当自愿地透露了我的秘密。此外,假设当他的大脑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他也会透露我的秘密,但这个事实却可能完全无法反映出他对我的忠诚度或其他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些针对我的态度使得我正在讨论的那些回应成为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回应。而为了具有这种意义,这些态度本身并不需要受到那个人的控制,并且他的这些人格特征也不需要是他应得的。应得的依据不需要本身也是应得的。
虽然正是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使得某些针对他的态度内容成为恰当的,但人格特征和态度内容之间的这些联系是规范性事实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惯例的问题。不过,当我们要确定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什么行动会被视为表达了特定的回应时,社会惯例便会发挥作用。用英语说“Thank you”(谢谢)是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这便是一个社会惯例的问题。此外,社会惯例会决定给某个帮助你的人送钱是在表达感激还是侮辱。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区分规范性事实和社会惯例在使得某些特定的回应成为恰当回应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假设某个人所做的事情使得表达某种态度(例如感激、钦佩、反对或谴责等)成为恰当的行为,并且假设按照我们的社会惯例,对这个人采取某种行动被公认为是表达这种态度的一种方式,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认为——那些共享这一惯例的人确实很可能将 认为,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使得对他采取这种行动成为了一种恰当的行为。就我正在讨论的那种应得的意义而言,这种对待方式看起来就是应得 的。
对于那些共享相关惯例的人来说,关于应得的这个结论是由一个重要的描述性事实推论而来的,并且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实纳入考虑之中才能理解在特定的社会中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例如,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如果某个行业的大企业高管通常都会获得七位数的奖金,那么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作为一个规范性的问题,上述的这种思路包含了一种错误的推论。因为我正在讨论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内在的规范性联系,并且它的范围只涵盖某种反应所表达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种联系会让那个内容变得并非不恰当。虽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但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论出:只要某种惯例认为某个行动表达了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行动便因此获得了证成。举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来说,谴责从邻居那里偷东西的行为可能会是恰当的。而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砍掉一个人的手便表达了相关的谴责,从而是应得的;换句话说,任何更轻微的惩罚都无法回应那种罪行的严重性。然而,这却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惯例认为,砍掉一个人的手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对于盗窃来说是恰当的,但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论出,砍掉已经被定罪的小偷的手是得到证成的。 [5]
应得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主张在“正面”回应的情况下甚至更有说服力,例如在赞扬和钦佩的情况下便是如此。某个人已经做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这个事实会使得赞扬和钦佩成为恰当的反应。但从这种关于恰当性的主张却无法推论出,某种特定的金钱奖励(甚至某种类型的金钱奖励)是不是它所要求的那种回应。
因此,在我看来,应得在对刑事处罚的证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刑事处罚涉及某种谴责,那么处罚就只有针对那些应得这种谴责的行动来说才是恰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罚必须是应得的。然而,尽管一种正义的制度可以对某些罪行施加诸如监禁等严厉的对待方式,但无论是在证成还是在限制这些严厉的对待方式时,应得的观念都没有发挥作用。对某些罪行施加严厉的对待方式并以此作为对罪犯的惩罚,这种做法只能通过这项政策的社会效益来获得证成;并且这种严厉的对待方式受到某种成本的限制,即为了促进这些效益,把这种成本施加在某个个体身上是公平的。此外,这种严厉的对待方式同样也受到这种要求的限制:它只能施加给那些拥有公平的机会来避免惩罚的人。而后一种要求就不是一种基于应得的要求。它并不是说,只有当人们所做的坏事是来自他们已经做出的选择时,他们才应得惩罚(在某种非制度性的应得意义上);而是说,拥有机会来避免某种负担是一种条件,并且这种条件在对任何社会政策的证成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一项政策为了提供某些普遍的社会福利而给一些人带来了负担,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拥有充足的机会去通过恰当的选择来避免承受这些负担。 [6]
当然,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即便刑事处罚并不仅仅由于它们表达了恰当的谴责才成为恰当的处罚,但我们也许能够以其他方式来依据应得而证成(和限制)刑事处罚。也就是说,也许有其他方式使得仅仅凭借某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就足以证成处罚。虽然我不认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我还没有提出论证来反对这类应得主张。在当前的讨论中,我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某类有效的纯粹应得主张(即关于某些态度的恰当性或不恰当性的主张),并指出这些主张能够证成的事物的范围。
这些结论同样适用于分配正义的情况。某个人在生产性的经济过程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个事实可能是我们对他产生钦佩之情或感激之情的理由。但这本身并不能使得某种特定水平的金钱奖励成为恰当的奖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如果按照某种习俗,那些发挥这种作用的人通常都会得到某种奖励,那么在一些人看来 ,这种奖励就是恰当的。但这些基于惯例的反应并不具有证成的力量(justifying force)。因此,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种特殊的应得主张——表达性的应得主张——在证成分配的份额时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然而,正如我刚才在刑事处罚的情况中所提到的,即使这种表达性的应得论证不能证成某些特殊的经济报酬,这里仍然遗留着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某些有效的、更具体的纯粹应得主张,并且它们关注的是人们应当获得哪些经济报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考察这些主张可能是什么,并根据到目前为止我所引入的区分来评估那些可能会支持它们的理由。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支持不平等份额的应得论证,这种论证主张,如果一些人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那么他们应得更多的报酬。例如,安东尼·阿特金森写道:“公平涉及努力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种可察觉的联系:如果人们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那么他们至少应得这些收入的合理份额。” [7]
为什么这一点看起来是正确的呢?对此的一个回答是,因为努力工作的意愿彰显了一种值得奖励的道德美德(moral merit)。而由于一个行动所体现的道德美德依赖于能动者在执行该行动时的动机,所以这一理由似乎要求我们应当把更高的工资提供给那些出于利他主义的理由而努力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为获得经济收益而努力工作的人。因此,这并不必然会产生曼昆所设想的那类影响。
道德美德对动机的依赖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很难去辨别人们的动机。罗尔斯援引了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一种要求奖励与美德相符合的原则是“不可行的”,而哈耶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8] 此外,从我们之前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道德美德的观念并没有为确定金钱奖励提供任何明确的标准。虽然道德美德可能应得赞扬和钦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某种特定数额的额外报酬提出了要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就对任何数额的额外报酬提出要求。
此外,我们可以说,也许基于某些同样的理由,奖励道德德性(moral virtue)不应当成为经济制度的职能。 [9] 在这里,经济制度的“职能”这个观念可能会有点含糊不清。但除了刚刚提及的那些理由,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理由来反对把按照道德美德进行分配看作是一种恰当的分配正义标准:因为一种分配正义的标准必须提供某种理由来支持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分配物,而且其他人应当接受这个理由并把它作为一个支持他们拥有更少分配物的理由;然而,道德美德看起来却没有提供这样一种证成的理由。虽然道德美德很可能本身就足以使得那些拥有美德的人应当获得更多的赞扬和钦佩,但这看起来并没有提供理由来支持那些更缺乏美德的人应当得到更少的收入。 [10]
这样一种理由似乎可以由以下这种观念来提供——虽然它与应得的主张相类似,但实际上却截然不同。这种观念指的是:如果穷人之前也做出了努力,那么他们就能够拥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较高收入,所以他们并不能针对他们的较低收入提出反对,因为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才导致他们未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尽管这种证成听起来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更多的努力应得更多的报酬,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或者说它至少不必如此。在这种证成中发挥作用的观念并不是应得,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充足的选择机会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choose)。即便某项政策会为更努力工作的人支付更多的报酬,但这项政策也可能基于其他非应得的理由而获得证成。例如,证成的理由可能是,这项政策所创造的激励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或者它让那些过得最差的人生活得更好,从而符合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只要正义的背景制度已被建立起来,那些没有通过努力工作来回应这些激励的穷人可能就无法抱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其他人更少。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是在某些并非不正义的条件下选择不去做出这种额外的努力,那么他们可能就无法提出抱怨。
这是罗尔斯在一段颇有争议的段落中提出的观点,我在第五章中讨论机会平等时也讨论了这一点,但我在这里将再次对它进行讨论,因为这个观点不但与当前的讨论密切相关,而且也很重要。罗尔斯在那个段落中写道:“即便某个人愿意做出努力和尝试,并因此在日常意义上是应得的,但这种意愿本身依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11] 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段话解读为包含这两个主张:(1)如果 某个人能够声称对这种做出努力的意愿具有功劳,那么这种意愿就是一种积极的应得依据并且它能够证成更多的报酬;但是,(2)如果这种做出努力的意愿是由某些诸如“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在他之外的因素”造成的,那么他就不能声称对这种意愿具有功劳。
但这种解读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把主张(1)作为一种对罗尔斯的解读是很难得到捍卫的,因为罗尔斯在其他地方反对过将道德应得作为一种分配份额的依据。 [12] 其次,主张(2)依赖于某种我已经表明是错误的观念,即应得的依据本身必须是应得的。
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那样,我们可以采纳另一种更好的解读。如果某种利益已经以合理的条款提供给某些人,并且这些人是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决定不要接受这些条款的,那么他们就不能抱怨没有拥有这种利益。正义原则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具体地阐明,哪些要求应当得到满足才能使得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变得“足够好”,也就是说,使得人们在这些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具有道德约束力。按照这种解读,罗尔斯在那个段落中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在说,如果做出努力的意愿本身是由(有利的)“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种意愿就不应得奖励;而是说,某个人缺乏 意愿去做出必要的努力以便获取某种利益,这一事实并不会导致这个人缺乏这种利益就是正义的,除非他是在符合正义要求的条件下不去做出这种努力。如果一些人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之中,并且他们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以便获取某些利益,而另一些人则生活在不仅更不幸福而且不正义的环境之中,并且他们没有做出那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的差异并不会导致由此形成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这一点说明了基于应得来证成不平等会不同于基于我所说的“充足的选择机会”来证成不平等,因为后者预设了一种关于正义的条件的标准。
为什么付出更多努力的人应得更多的报酬,对此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努力涉及牺牲,而牺牲应当得到补偿。但除了要求付出更多的努力,某些工作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涉及更多的牺牲。例如,有些工作会比其他工作更不愉快或更危险,或者会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支持给予更多报酬的这一理由并不会只让那些从事费力的白领工作的人受益,他们甚至不是主要的受益者。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讨论之中,这种解释存在着两个问题(它们并不必然构成对这种解释的反驳 )。第一,按照这种解释,对补偿的要求并非基于某种应得的观念,而是像前面讨论过的需求主张一样,它们建立在某种收益(或损失)的观念之上。第二,对牺牲进行补偿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正义标准(不管它是否基于应得),而是一种局部的原则,并且它预设了某些其他更基本的标准。例如,它可能预设了这种观念:如果人们受到了伤害,那么他们应当获得补偿。但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会假定相关的标准是某些关于分配正义的观念。
如此一来,对补偿的要求背后所体现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应用分配正义的相关标准,我们在评估人们的福祉水平时,需要考虑诸如付出特别的努力等牺牲所带来的福祉损失。现在让我们假设,这种正义的标准要求人们的福祉水平必须符合某种模式(它可能是平等,也可能是某种非平等主义的模式)。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标准,如果某个结果只有当它不考虑努力(或某些其他种类的牺牲)的成本时才会符合这种模式,那么这个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正义的。为了实现正义,做出这些牺牲的人应当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 益处(例如更高的收入),以便对这些牺牲进行补偿,从而使他们达到正义所要求的福祉水平。因此,如果相关的正义标准要求人们必须达到平等的福祉水平,那么为了实现正义所要求的那种总体的平等,不平等的收入也许就会是必须的。
对努力的重要性的另一种解释是,努力代表了人们在合法期待获得某种报酬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而合法的期待不应当遭到落空。这里的要点不在于牺牲要求获得补偿,而在于正义的制度必须实现它们用来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的那些期待。然而,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合法期望的主张预设了某种制度合法性的标准。因此,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努力会导致它无法成为一种评估制度的独立依据。
正如曼昆所指出的,应得的另一个观念是:“人们应当得到与其贡献相一致的报酬。” [13] 当不同参与者的“贡献”可以被清楚地区分时,这种观念看起来最具有说服力。例如,假设两个人一起合作生产某个产品,其中的一个人负责生产内部构件,另一个人则为它添加一个设计独特的外包装。如果内部构件所产生的功能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基本相同,但是独特的设计却让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更畅销,并且为他们挣来了很多钱,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负责这种设计的人对产品的成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此他应当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
但在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形式中,不同参与者的贡献并不容易区分。 [14] 曼昆似乎把某个特定参与者的贡献——他的报酬应当和它“相一致”的那种贡献——等同于该参与者的“边际产品”(marginal product)。在此,边际产品指的是,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该参与者的工作所引起的生产价值的差异。但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纯粹的虚拟观念未必会与下述这种贡献观念相一致,即从适用于我的第一个例子的那种意义上来说,某个特定参与者“已经做出的(那种)贡献”。 [15]
假设某个生产过程涉及许多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偶尔会看不到别人正在做什么。如果有某个人站在一个能看到所有工人,而且也能被所有工人看到的地方,然后向这些工人发出信号,以便告诉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最需要去做什么,从而帮助工人协调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人可能会工作得更有效率(即在给定总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工作)。而这位协调员的边际产品将等同于他在一个时间单位内的“指导”所增加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他的边际产品指的是,在一个时间单位内,工人在他的指导下所生产的商品与没在他的指导下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异。也许这个人在这种指导职务上的边际产品比普通工人的边际产品更大。然而,虽然这种指导使得某些额外数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但这些商品并不是由提供这种指导的人“生产”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由其他工人在他的帮助之下生产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是,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在理性的范围内会为这个工人的服务所支付的最高边际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工人没有获得这个报酬,他就受到了欺骗,或者“被剥夺了他的劳动成果”。 [16]
在这个例子中,我假定提供指导的那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要求任何特殊的技能。他只是站在一个不同于其他工人的地方,因此能够看到在特定的时间内工人需要从事哪些工作来保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拥有某个特殊的技能才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比方说他能够快速地辨别如何最好地推进工作,那么情况看起来会有所不同。拥有这种技能可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对于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社会而言,投资某些培训以便让人们能够发展出这种能力,并且挑选出那些已经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来担任这种“指导”的职务,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而这种指导的职务可能会比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工作更令人向往,因为它对体力的要求更低,并且提供了“职位的权力和特权”以便担任者能够行使这种已经展现出来的能力。因此,创造这一职位并提供担任这一职位所需的培训,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而进一步的问题是,除了这种不平等之外,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是否应当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报酬;尤其是,是否因为他的边际产品比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更高,所以他应当得到更多的报酬。在我看来,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某个特殊的技能是必需的技能,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以下这个事实:“指导者”的“边际产品”仍然只是一个纯粹的虚拟概念,就像我之前所举的例子一样。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种观念之中,即人们可以基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而应得更多的经济报酬。为什么这一点是正确的呢?这些能力又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在艺术、科学和工程上的某些能力,也许还包括组织和管理上的能力,可能是值得我们赞扬和钦佩的优异特征。但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从这一点并不能推论出:这些能力对某种特定的经济报酬提出了要求——它们甚至根本没有对任何经济报酬提出要求。
另一方面,某些职位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特殊机会,甚至是特殊的经济报酬,可能是基于它们所带来的好处而获得证成的,例如因为它们提高了经济效率,或者因为它们满足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或其他分配正义的标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论证来支持这一点(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这种论证):我们应当根据人们的能力来为这些职位选拔人才。此外,如果那些拥有相关能力的人被这些职位所选中,那么他们因此也可以说是应得的。“能力”在与此相关的意义上并非指的是一些人所拥有的某种有价值的内在特征,而是以一种依赖于制度的方式被定义成这些特质:无论这些特质可能是什么,它们会让某个人有可能在相关职位上表现良好。基于应得而要求获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制度资格的要求,而不是一种应得的要求。
在这一章中,我讨论了应得的观念是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依据来证成不平等的报酬或对它们施加某种限制。而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应得的观念需要与“人们应当拥有什么(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这一极其广泛的观念有所不同。此外,基于应得的证成若要具有独特性,也需要与以下这两类证成有所不同:第一类证成依赖于某些制度所做出的规定,并且这些制度以其他方式获得了证成;第二类证成则基于以某些方式来对待人们会带来好的结果。虽然某些纯粹的应得主张是有效的,尤其是那些关于人们应得赞扬、感激、责备或谴责的主张,但我已经论证过:无论是有差异的经济报酬还是特定形式的刑事处罚,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
随后我考察了针对额外报酬所提出的各种具体的应得证成,包括基于道德美德、努力、能力和贡献的证成。在每一种情况下,我的策略都是先考察为什么这些特征看起来是特殊报酬的依据,然后提出论证来表明:经过更仔细的审视,这些特征都没有为特殊的经济收益提供一种有效的应得证成。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所有以应得的术语进行表述的平等主张都是假的或错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些主张很多都是相当正确的。我质疑的是,这些主张是否建立在应得这一独特的道德观念之上。
例如,考虑一下我刚刚引用的安东尼·阿特金森的那句话:“如果人们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那么他们至少应得这些收入的合理份额。”对这句话的最佳解释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非制度性的应得主张。一个可辩护的经济体系必须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去赚取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虽然这种机会对穷人来说特别重要,但它对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如此。剥夺人们这种增加税前收入的机会是不公平的,而以税收的形式来取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则体现了双重的不公平(它还违背了合法的期望)。阿特金森关于人们通过工作 更长的时间或更努力地工作来寻求变得更富有的例子特别强有力地说明了后一点,而这可能意味着他对提高有效税率的反驳只适用于劳动收入所得税。但是,只要某些制度允许人们通过投资来获取收入,并且这些制度已经独立地获得了证成,那么我们便能够以人们放弃消费去投资赚钱作为例子来说明同样的观点(即关于合法期望的观点)。
[1]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331-5.
[2] 参见Feinberg, “Justice and Personal Desert,” 81, 85-8; 以及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section 48,他引用了范伯格的观点。
[3] 在Moral Dimensions , chapter 4和“Giving Desert its Due”,以及更近的“Forms and Conditions of Responsibility”,我用更长的篇幅捍卫了这些主张。
[4] 更充分地讨论这些关于责任的主张,可参见脚注3中所引用的著作,尤其是“Forms and Cond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5] 在我看来,当代美国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人们在以下这两个方面的惯例观念已经经历了一种达到道德灾难程度的通货膨胀:一是对于某些经济职务而言,哪种水平的经济报酬是恰当的;二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犯罪而言,哪种监禁判刑才是恰当的谴责。
[6] 对这种解释(即“选择的价值”)的详细阐述和捍卫,参见chapter 6 of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和“Forms and Cond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7] Atkinson,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 186.
[8]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274.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93-4.
[9] 我并没有否认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所正确指出的这一点,即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制度资格的应得观念(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 chapter 7, 142-3)。例如,假设某个跑步运动员在终点线之前被一阵大风绊倒了,从而没有获得胜利,因此也没有资格获奖。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他应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因为实际上他跑得更出色。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比赛应当被组织得更好,以便让更出色的跑步运动员更有可能获胜。但这是因为比赛的用途是充当运动能力的竞赛活动。我的观点是,任何此类非制度性的应得观念都不应当作为确定经济报酬水平的依据。而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第139-140页),这个观点所涉及的内容是经济制度的性质和证成,它并非由应得的概念推论而来。
[10] 塞缪尔·谢弗勒指出了这一点,参见“Justice and Desert in Liberal Theory,” 191。
[11] A Theory of Justice , 74 (2nd edn, 64).
[12] 参见A Theory of Justice , section 48。
[13]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32.
[14] 正如皮凯蒂所论证的那样:“事实上,它(即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变得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建构,而在此基础之上,一种对更高地位的证成便可以被详细地阐述出来。”(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p.331.)
[15] 参见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187n.和Amartya Sen, “The Moral Standing of the Market,”15–17, 以及“Just Deserts”,等等。我认为诺齐克的观点是(正如我刚刚引用的那个脚注的最后一句话所表明的):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人们获得与其边际产品成比例的报酬,这个结果之所以会是正义的,是因为它来自一个自由交换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符合正义的资格概念,而不是因为这些报酬与边际产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16] 正如森(Sen)在《正义的应得》(“Just Deserts”)中所指出的,当某个人的“贡献”只是允许别人使用他所拥有的某个东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清楚。例如,假设某个人拥有一块狭长的土地,它夹在一个场地和一个工厂之间。而如果在那个工厂就业的工人可以穿过他的土地而不是绕道而行,那么他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因此,这个人在诺齐克所说的“虚拟”意义上的“贡献”(即由他允许别人穿过他的土地产生的差异)可能非常大,即便他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
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已经大大加剧。2014年,美国收入总额(来自薪酬、利息红利和销售利润)的21.2%流向了收入处于前1%的人,而收入总额的4.9%则流向了前0.01%的人。这是不平等的一种显著的加剧。此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年至2014年之间,前1%的人的税前收入增长了174.5%,而后20%的人的税前收入仅仅增长了39.7%。(在这些情况下,收入包含了诸如福利金之类的政府转移支付。)税后收入的增长差异甚至更加尖锐:前1%的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00.2%,而后20%的人的税后收入只增长了48.2%。(收入处于后21%和后80%之间的人的增长率只有40%。)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即2014年),前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为6 087 113美元,总体上是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20倍。 [1]
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反映出许多不同的现象,包括:第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皮凯蒂称之为“超级管理者” [2] )的薪酬在增加;第二,金融领域的盈利能力在上升和增长;第三,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资本回报(returns to capital)的形式。
关于第一个现象,我在第一章中提到了这些事实: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之中,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平均薪酬的20倍。这个比例“在2000年达到了376∶1的高峰”。2014年,这个比例是303∶1,“高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的任何时期”。 [3] 此外,“从1978年到201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高管的)薪酬增长了997%,几乎是股市增长的两倍,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员工的年薪的缓慢增长,因为后者只增长了10.5%”。 [4] 这种程度的不平等看起来显然会令人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为什么它应当令人感到不安,以及这是否可以用我在前面几章讨论过的那些反驳来加以解释。
首先考虑一下那些基于不平等的后果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在我看来,上述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并不在于它会造成那些应被反对的地位伤害。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当下美国的穷人确实遭到了这些伤害,即遭到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但是,这看起来并不是由超级富豪的高收入造成的,也不是由他们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富人确实过得和我们其他人(尤其是极其贫困的人)非常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设定的标准并不会使得我们有理由感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对这个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穷人遭受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所参照的标准是由“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设定的,而不是由超级富豪的生活方式设定的。因此,这种不平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会产生某些应被反对的地位差异。
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会威胁到人们获得优势职位的机会平等。这在1970年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严重了。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确保高等教育和更广泛的优势职位在选拔人才时要实现程序公平之外,我们还需要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幼儿发展条件。
这些目标都很难实现,而不平等的加剧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接下来我会谈到这一点),从而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更难以实现,譬如它可能导致公立学校更难获得适当的资助。然而,如果这些目标都得以 实现,那么尽管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在近期增加了收入并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否会威胁到机会平等。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教育费用的支出是有限的,而这可能会给富人的孩子带来重要的优势,即便他们置身其中的那个体系在其他方面是公平的。但是,近期的不平等加剧可能会威胁到广义上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关注的是人们在市场上通过创业来展开竞争的机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创造了一类极其富有的家庭,他们能够获得其他人完全缺乏的资本。
现在我转到政治平等的问题。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之所以在近期增加了收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治决策造成的,这些政治决策包括:法律和政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金融行业的监管减少了,以及税法的改变降低了针对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也降低了遗产税。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反映了富人对政治拥有过多的影响力。就此而言,近期的不平等加剧主要来源于人们先前早已 在影响力上形成了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政治结果产生了影响。
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富人和其他人对于影响政治结果所能够投入的资金会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而这会导致那些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观点更有可能反映富人的利益,这是因为要么这些公职人员本身就很富裕,要么他们是由于得到富裕捐助者的支持才被选中的。作为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公平,这种情况本身就应当遭到反对;但它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还因为它导致了政治结果更难以满足正义的其他要求,例如平等关切和实质机会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在我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针对不平等加剧的反驳中,我认为这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反驳。
另一种强有力的反驳是,这种程度的不平等会导致富人对穷人的生活拥有某些不正当的控制权。除了刚刚讨论过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反驳还包含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而这种反驳对于皮凯蒂强调的第三种不平等而言——资本集中在少数极其富裕的家庭手中——尤其是正确的。
这些基于不平等的后果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并不能解释许多人的这种感受:近期的不平等加剧除了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外,它本身也应当遭到反对。为了评估这种反驳,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观念,即收入不平等可以仅仅基于不公平而遭到反对;此外,我们也需要考察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公平观念。
如果某个商务企业的合伙人在金钱和时间上都进行了相同的投资,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一个公平的利润分配机制应当给予每个合伙人同等的份额。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与此相类似:它也是一个互利的合作企业,而社会成员作为这个企业的参与者,也应当得到与其贡献成比例的回报。然而,即便在这个假想的公司情形中,我们有理由支持同等的份额,但这个理由并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存在着以下这两个原因。
首先,我假定公司的成员在金钱和时间上都做出了相同的投资,并且我们还可以补充道,他们在才能上也做出了相同的投资。对此人们可以反驳说,这些假设并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因为社会合作的参与者对资源和能力的贡献极其不同。其次,更根本的是,把社会和公司进行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合作并不是个人加入某个企业并在这个企业中贡献出他们事先被界定好的资源和才能。个人拥有哪些资源、什么才能算是经济上有价值的才能,以及个人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发展哪些能力,这些问题都是由社会制度来决定的——社会制度既包括那些确定财产权和诸如有限责任公司等经济组织形式的法律,也包括那些在这个框架内产生的特定制度。这些都是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结构需要成为什么样子才会是公平的。因此,对相关的公平观念的详细说明就不能依据某些依赖于此类特定结构的所有权观念。
然而,社会成员作为合作计划的参与者,这个主张在回答上述那个问题时能够发挥某种作用。在确定社会合作规范时,我们需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利益,尤其是他们从占有更大份额的社会合作成果中所获得的利益,并给予这些利益平等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假定他们必须拥有平等的份额,而只是假定在回答“确定这些份额的过程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考虑他们的利益。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差别原则的论证便表达了这种观念的某种形式。他论证道,如果一个社会的合作成员在不知道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情况下会选择某些分配原则,那么这些分配原则就将是公平的。 [5]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是在“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中被挑选出来的,而他在关于“原初状态”的论述中,更具体地阐述了上述这种观念。 [6]
按照罗尔斯的定义,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指的是处在特定社会地位上的公民或公民代表。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这些人的动机只是尽可能地让他们自己或他们所代表的人受益。但是“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使得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具有哪些特殊的才能或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这种动机假设体现了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这些人从更大的份额中所获得的利益被纳入考虑之中;而无知之幕则体现了在确定那些原则时,这些利益具有平等的地位。
罗尔斯论证道,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某项原则会导致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所获得的利益比在平等的分配下更少,那么他们将没有理由接受这项原则。因此,要求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人都获得平等的报酬,这个原则就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第一解决方案。但是,这些相关人员却有理由偏离这个“平等的基准”(benchmark of equality),因为如果不平等并不会导致他们过得更糟(假定诸如基本自由之类的其他因素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些不平等。因此,罗尔斯得出了这个结论: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将选择他的差别原则作为分配正义的标准。这一原则主张,某个基本结构S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正义的:这个基本结构S所涉及的不平等有利于社会地位最差的那些人;也就是说,任何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替代方案都不能使得社会地位最差的那些人在这些替代方案之下过得比在S之下更好。 [7]
假定我们能够以一种增加或至少不会减少工人收入的方式来减少CEO在我们当下体系中的收入(这个假定看起来是非常可信的),那么差别原则将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所描述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然而,这种解释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困惑:很多人即便没有接受任何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或他对差别原则的论证一样苛刻的要求,但仍然认为我所描述的那种不平等程度应当遭到反对。对此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人并不确定公平提出了哪些精确的要求,但他们认为,不管 对公平的正确解释是什么,这些特定的结果都不能被称为“公平的”。 [8] 这便引起了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否以其他方式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所引起反对的不公平之处;第二,这种解释与罗尔斯给出的解释有什么关系。
按照我对不平等所持有的关系性观点,正如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关于不平等的纯粹事实,而是那些产生不平等的制度。 [9] 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必须采取某种特定的模式才会是正义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我认为,即便是在单独某家公司的情况下,一般而言,管理人员、工人和股东的收入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比例也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答案。恰恰相反,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机制不能以正确的方式来获得证成时,不平等才应当受到反对,并且也是不公平的。 [10]
因此,我将从这种观念来展开我的讨论:如果某个制度在收入和财富上造成了巨大的差距,并且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差距,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平等可以被称为“任意的”,意思是它们缺乏恰当的证成。从这个起点出发,接下来我们可以具体地说明哪些理由是支持收入不平等的好理由,以及哪些理由不是这种好理由,并以此来为“公平制度”的概念添加内容或至少对它进行限制。(这意味着,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理由,那么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 就无法得到证成。)我将首先考虑那些造成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可能会以哪些方式来获得证成,之后再回到税收的问题。
基本结构的某些构成要素会产生税前收入——我在第七章中把这些要素称为“‘预分配’体系”,而对这些要素的证成必须考虑到所有依赖这个体系维生的人 [11] 想要获取更大份额的资源的理由,也必须把个人自由的考量纳入考虑之中。这些考虑因素既包括人们有理由想要获取更大范围的可利用选项,也包括他们有理由反对受到别人的控制。这可能还包括哪些其他的理由呢?
在第四章中,针对那些具备不平等优势的职位,我为它们提供了一种三层证成;而在讨论三层证成的第一个层次时,“为了论述的完整”,我允许这种证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某些独立于制度的财产权观念或应得观念。我在后续的章节中提出论证把这些备选方案都排除掉了。例如,我在第八章中论证过,任何独立于制度的应得概念都无法发挥这种证成作用。而在第七章中,我已经论证过,任何非制度性的财产权都不能作为证成或批评经济制度的依据。然而,可以作为这种依据的理由则包括某些个人利益——这些利益导致人们认为存在着非制度性的财产权,例如人们有理由想要确保他们的各种个人财产的稳定性,以及包括某些由制度界定的权利——这些权利基于这些利益而获得了证成。
诺齐克关于威尔特·张伯伦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威尔特和他的粉丝之间的交易可能会导致不平等加剧。但正如诺齐克所说的,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不去干涉这种税前收入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仅仅来自威尔特行使他的权利以决定是否要按照某个给定的价钱去打篮球,以及他的粉丝行使他们的权利来花钱买票去看他。(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论证过的,对威尔特的收入进行征税是否具有合法性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像反对企业高管和金融家的收入那样去反对体育和娱乐明星的高收入。这并不是因为如曼昆所建议的那样, [12] 这些体育和娱乐明星的税前收入被认为是应得的(在此,应得被理解为优先于制度并且能够用来证成这些制度所分配的报酬)。倒不如说,这些税前收入之所以没有遭到反对,是因为就像诺齐克所设想的威尔特·张伯伦的收入一样,这些税前收入也被认为仅仅来自某个服务的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自愿交易(而不是由于法律创造了知识产权和有线电视的垄断),并且干涉这种交易是错误的。
不平等是由人们行使经济生产力所必需的那些权利和权力造成的,这一事实也可能用来证成不平等。一个基本结构并非仅仅分配某些独立存在的利益。 [13] 它还会创造和鼓励某些互动形式,而物质利益正是通过这些互动形式而被生产出来,因此它也是一个生产利益的体系。如果某些特征对生产利益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平等是由这些特征造成的,那么这一事实原则上可以用来证成不平等。 [14] 但由谁来享受这些利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某个权利体系会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促进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管那些增加的利益如何分配,这个事实都会被认为是在支持这个权利体系。例如,如果那些增加的利益都归总统所有(并且这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某个生产性的权利体系会促进发展,这一事实就不会被认为是在支持这个权利体系。因此,仅仅说那些从不平等受益的人能够 以一种会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方式去补偿那些失败者,这是不够的。 [15] 基本结构产生不平等的那些特征至少必须能够使得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会让每个人实际上 都过得更好。
这两种可能性可以组合成基本结构产生重大不平等的那些特征的必要 条件:要么消除这些不平等会侵犯到重要的个人自由 [16] ,要么这些不平等是经济体系要以一种让所有人受益的方式去运作所必需的。而缺乏这两种理由支持的不平等会以某些方式让担任某些经济职位的人受益,并且这些方式是其他人没有理由去接受的。从前面提及的那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利益可以说是“任意的”:为什么要让这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受益,这里并不存在着任何充分的理由。
这个析取条件是对罗尔斯的这个观点的一种相对较弱的解释,即产生不平等的体系必须“对每个人都有利”。 [17] 罗尔斯更喜欢把这个观点解释成“差别原则”,它是一种更强的解释。差别原则不仅要求产生不平等的体系必须让所有人都受益,而且还要求必须让那些拥有较少利益的人尽可能多地受益。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减少某个体系所产生的不平等,从而让那些拥有较少利益的人受益,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过度的”。 [18] 然而,即便我所说的这种较弱的要求也是相当强有力的。它足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接受某个像罗尔斯所提议的那么强的原则,但他们依然会认为我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些不平等应当遭到反对。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是由我们的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造成的,并且这些特征只让富人受益。
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这依赖于那些关于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它如果做出某些改变将会如何运作的经验事实。这是我所提出的公平概念的一个普遍后果。不同于其他替代概念——它们把公平或正义等同于某种针对结果的特定模式,我提出的这个概念使得关于公平的结论依赖于这些复杂的经验问题:经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果它们的安排方式有所不同,那么它们将会如何运作。(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也具有这个相同的特征。)基于这个原因,比起前几章中那些更彻底的规范性考察,接下来我关于当前的不平等形式是否公平的讨论将更具有推测性。我的目标是根据我提供的观点来确定当前收入不平等的证成性所依赖的经验主张。
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种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涉及这些不同的现象: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金融领域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在增长,资本回报率在增加,以及由继承而来的财富也在增长。接下来我将以第一种现象作为例子来集中进行讨论。这种收入的差距是由这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那些决定以及压低工人工资的因素,二是那些决定高管的薪酬并允许增加这些薪酬的因素。首先,让我们考虑那些影响最高收入的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公司的高管薪酬已经大幅地增加了。从那时起,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技术的改变、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最大公司的规模扩大。有人可能会说,公司规模的扩大提高了这些公司高管的边际生产力,从而证明了增加他们的薪酬是正当的。但基于以下这两个理由,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证成:首先,正如皮凯蒂所观察到的,我们很难去界定那些担任这种职位的高管的个人边际生产力。 [19] 其次,更根本的是,即便我们能够在纯粹虚拟的意义上来衡量高管的边际生产力(即衡量由他们出色的工作表现和糟糕的工作表现造成的差异),但这种纯粹虚拟意义上的边际生产力本身并不能证明更多的报酬是正当的。正如我在第八章中论证过的,虽然去掉某个人的工作会带来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确定某种由这个人(相对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其他人而言)生产出来的产品。
我已经说过,经济体系产生严重不平等的那些特征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获得证成:为了使该体系以一种让所有人受益的方式去生产利益,这些特征是必需的。而公司需要有权力来选择它们的高管并决定支付多少薪酬给他们,而且有人可能会主张:当下的高管薪酬水平是人们合法行使这些权力的结果,因为人们需要用这些更多的报酬作为激励来吸引有才能的人去担任高管的职位,并激励他们在这些职位上拥有出色的表现。然而,正如比文斯和米歇尔所指出的,证据表明:如果薪酬的标准有所不同,并且高管普遍得到远远更低水平的薪酬,这些职位仍然会吸引那些有才能的人。 [20] 此外,正如他们也指出的那样,一家大公司CEO薪酬的上涨和下降所反映的是该公司所在的那个一般领域的公司股价,而不是该公司在那个领域内的相对成功。因此,奖励所针对的是并不是管理决策的质量,而是这种运气,即幸运地处在一个公司总体表现良好的经济领域。
技术的改变、全球市场的增长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已经对所有工业化的社会产生了影响。但是,高管薪酬的增长在某些社会要比其他社会大得多:一般来说,英语国家的增长更大,而美国的增长则是最大的。 [21] 正如皮凯蒂所建议的,这使得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近期高管薪酬的增长受到了这两种因素的强烈影响:一是被这些国家所接受的、适用于这些职位的薪酬标准;二是这些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高管的薪酬越来越多地由薪酬委员会来决定,并且这些委员会通常会雇用外部顾问,而这些顾问则依据高管在“具有可比性”的公司所获得的回报来推荐和证成薪酬方案。 [22]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不平等是不正当的,这一结论并没有依赖于这个假设,即高管薪酬是由某种假公济私的腐败造成的。我所说的内容与下述这种情况完全是相容的:薪酬委员会与那些由它们来决定其收入的高管确实是互相独立的,并且这些委员会是根据它们认为在客观上有正当理由的标准来进行运作的。倒不如说,这里的要点是,导致他们增加薪酬的那个机制缺乏恰当的证成。而如果一个决定高管薪酬的机制具有这种严重的“疏忽”,那么它对于公司的良好运作来说就不是必要的,并且改变这种机制以减少不平等,也不会不正当地减少个人的自由。
并不是只有美国最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才会遭到这种反驳。许多其他收入(包括大学教授的收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惯例的标准来决定的,而不是制度的良好运转所必需的。CEO薪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涉及的收入的规模。这表明,对不平等的这种特定反驳(亦即“任意性”的指责)所具有的强度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程度是成正比的。
高水平的高管薪酬缺乏证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会破坏那些反对向这种收入征税的意见,例如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些税收会干扰经济效率。但这里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哪些理由会支持 以高税率对这些收入进行征税。第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获得证成需要满足某些条件——例如平等关切和实质机会所要求的条件(稍后我会继续讨论它们),而要为这些条件所需的公共物品买单,税收则是必不可少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已经降低了,这是更广泛的减税政策的一部分,而减税政策破坏了政府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仅仅针对那些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征收更高的税款,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些税收将是任何可被证成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对最高收入者征收高边际税率的第二种可能的证成是,为了减少不平等的负面后果,例如减少它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高边际税率是必需的。在此我将不继续讨论这种证成,因为我已经讨论过那些基于不平等的影响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
第三种可能的证成则是,仅仅为了阻止那些本身不公平的不平等,我们也需要对高收入进行征税。虽然这种证成有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税收,即便它们这么做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理由,也不需要以这种更有争议的方式来获得证成。这种证成在这种情况下所主张的是,只有当一部分税前收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时,基本机构产生税前收入不平等的那些特征才是可被证成的。这种证成的合理性依赖于对以下这个问题给出某种解释,即为什么这些税前收入一开始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并且不能受到限制。
我们刚刚讨论的高管薪酬的情况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例子。公司需要有权力来决定雇用谁担任高管以及决定这些高管的薪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监管这种权力以阻止高管薪酬的不正当增长,那么遏制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假设我们有其他理由来这么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这些收入征收重税。而如果正如一些人所表明的, [2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边际税率下降是高管薪酬增长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给予了高管更大的激励去寻求更高的薪酬和奖金,那么提高这些税率就将是遏制这种增长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会减少这些激励。
现在我开始讨论那些影响工人收入和更广泛的穷人收入的因素。在我提议的框架之内,这里的问题是:为了让经济生产力有利于所有人(包括工人和穷人),那些通过压低工人和最贫穷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是不是必不可少的。鉴于当代美国的经济体系,工人在公司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要么取决于公司和工人个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工人普遍没有议价能力;要么则取决于公司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讨价还价,且工会能够以罢工作为威胁来支持自己。这意味着,结果的不平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的有效性,而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那段时期,工人的工资之所以没有比实际情况增长得更多,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法律和政策削弱了这种议价能力。 [24] 工会力量的下降只是近几十年来穷人普遍过得不好的原因之一,因为许多穷人都失业了。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5]
作为回应,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工会拥有更大的权力会干扰经济效率,例如它会导致工人有能力阻止某些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可能为限制工会的权力提供了一种证成,即便这会降低工人的收入。但是,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体,事实上没必要以一种将工人的收入份额降低到这种程度的方式来削弱工会。然而,即便那些降低工人的议价能力并因此降低他们的收入的因素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但按照我提倡的观点,这一点只有当这种生产率有利于所有人(包括那些收入减少的人)时,才可以用来证成结果的不平等。而我已经引用的那些数据则表明:最近几十年来,生产率的收益实际上并没有被最低收入群体所共享。那些在美国收入分配中处于后50%的男性,他们在2015年的实际税前收入并没有高于1962年。 [26]
一些人可能会争论说,考虑到国际竞争,提高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并不会让他们过得更好。恰恰相反,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相关商品的价格,结果会导致那些雇用他们的公司不再具有竞争力,而工人也将因此失去工作。然而,即便这为降低工人的工资提供了一种证成,它也没有证明降低工人的收入 是正当的。如果低工资会让公司保持盈利,那么这些利润可以由工人来共享。这一点可以通过让工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来实现,或者通过让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持有股份的所有权来实现,而该基金将使用这些利润来为收入补助或我已经提到的其他措施买单,或者将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公共交通和免费高等教育,从而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更不需要依赖于他们的收入。 [27]
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看成不仅涉及收入的不公平分配,而且更广泛地涉及经济生产力成本的不公平分配。为了建立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公司需要有能力随着条件的改变去雇用和解雇工人。但是,这里并不存在着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灵活性的成本应当只由工人来承担。只要这个问题是财务上的问题(即工资降低以及由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失业补助体系或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来解决。但我们正在讨论的成本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成本。当一家工厂倒闭了或转换成另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时,被解雇的可能性会剥夺人们对其生活的控制权。为那些被解雇的工人提供有效的再培训项目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是,只有当完成这些项目的工人能够获得工作时,这些才是有用的。因此,一种充分的应对方案还必须包括那些刺激需求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措施,例如货币和财政政策。
总结这一讨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让某些工人来承担经济生产力的成本会造成某种不平等,而要阻止或至少缓解这种不平等,我们起码需要采取以下这三种措施:一是某种形式的财政缓冲,例如失业补助或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二是下岗工人能够在其中获得新技能的有效项目;三是某些更广泛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会为那些获得相关技能的工人提供新的就业形式。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的费用,某些税收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税收能够以我提到的第一种方式来获得证成: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获得证成需要满足某些条件,这些税收可以用来支付这些条件所需的费用。那些压低工人收入的现行政策是不公平的,这一指责依赖于这个主张,即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实施这些措施,并且这会让工人比在现行体系下过得更好。
我之前区分过三种针对不平等的反驳,而支持这些反驳的理由在这里都汇合在一起了。我一直在讨论的反驳是这样一种反驳:对生产效率的成本的某些分配是得不到证成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工人能够通过某些项目去获得新技能,这一点不只受到这种公平要求的支持,我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支持实质机会的理由同样也会支持这一点。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职业并且发展这些职业所需要的技能,这些理由并不会在一个人接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后就消失了,而是会贯穿他的一生(不管他是否失去那份工作)。 [28] 另外,如果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职责之一是管理经济以确保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那么下述这种做法就会违背我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种平等关切的要求:某些工人所在的经济领域或国家地区因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处于失败之中,但比起这些工人而言,政府更充分地向其他人履行了这一职责。当然,找到某些方法以便更公平地分配经济生产力的成本,这是非常困难的。 [29] 然而,除非存在着有效的政治意愿来支持这项任务,否则人们甚至不太可能去尝试它;但反过来,当工会的政治力量薄弱,并且经济不平等会对政治影响力产生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的那些影响时,人们则不太可能会形成有效的政治意愿来支持这项任务。
我一直在讨论高管与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这只是近期不平等加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我将使用我刚才描述的那个规范性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答案将依赖于有关金融机构筹集和分配资本的必要性,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特定金融工具的证成性等经验问题,而我无法在此对它们进行探究。 [30]
然而,我确实想谈一谈我提出的框架如何应用到继承财富的情况,这是我提到的不平等的最后一个来源。在这里,我们自然而然会从这样一种观点来展开讨论: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积累的那些资产都是以合法的方式获得的,那么这个人就有资格将这些资产传递给他的子女,就像他可以采取任何其他方式去自由地花钱一样。然而,以这种简单的形式来陈述这个主张,这过于仓促了,因为它简单地假定了一个人对于资产的资格包含了通过遗产来转移资产的权力。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这是人们去工作和存钱的主要理由之一。因此,人们拥有某些基于自由的重要理由来支持应当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去转移一些资产。与此相反,为了限制不平等的不良影响,人们也有理由去抑制不平等。这些理由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强(也可以说,允许代际转移的理由变得越来越弱),并不是基于被转移的总资产的规模,而是基于转移到任何单一个体身上的金额。
因此,为了实现减少不平等和限制对资本的集中控制这两个目标,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对遗产的继承人进行征税,而不是不管遗产如何分配就直接对遗产本身进行征税。这里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像对其他来源的收入一样去对由馈赠和遗产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 [31] 像其他任何税收一样,这些税收也需要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支持这些税收的理由跟我在其他情况下所讨论的理由是相同的,这些理由既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的必要性(尤其是为了满足实质机会和平等关切的要求),也包括支持限制不平等以抑制其不良影响的那些理由。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对资本的集中控制,那么正如皮凯蒂所建议的,通过对财富本身进行征税,而不是仅仅对财富的代际转移进行征税,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32] 而只要我们关注的是对经济的控制,那么这种税收就可以集中在资本 身上;在这里,资本指的是那些涉及控制经济的财富形式,而不是诸如主要住宅的所有权之类的一般财富。 [33]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即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比率以及大公司中工人和高管之间的收入比率。这些比率以及它们的增长方式是令人不安的。我已经论证过,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比率本身,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它们令人不安,也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关于这些比率应当是什么的特定看法。倒不如说,问题在于造成这些不同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缺乏证成的,并且我已经试图阐明这一点怎么会这样。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以同样的方式来确定正义的问题。差别原则并没有详细阐述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人之间的期望比率必须是什么,而是详细说明了产生这些期望不平等的制度必须以何种方式来获得证成。由罗尔斯的原则可以推论出,我所描述的收入不平等是不正义的。但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没必要接受某个像罗尔斯的原则一样强的原则。相同的结论也可以从我所说的这个较弱的必要条件推论出来:不平等为了能够获得证成,它们必须是由人们行使重要的个人自由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或者是由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导致的,并且这些特征是经济体系以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方式去运作所必需的。
然而,支持这个较弱主张的理由会自然而然地导向某种非常类似罗尔斯的更强原则的东西,即要求可被证成的不平等不仅必须让那些拥有较少收入的人受益,而且必须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受益。 [34] 即便基本结构的某个特征会产生不平等并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所有人都受益,也就是说,它的影响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但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却仍然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据我提议的观点,它的不公平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以其他方式来获得相同的生产优势,并且同时更平等地分配利益。因此,如果这些产生不平等的特征缺乏其他的证成,那么它们就将是“任意的”。所以,消除所有在我描述的那种意义上的任意不平等就将得出某种非常类似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东西。但是,为了谴责现有的不平等程度,我们没必要一直追随这个论证直到得出这一结论为止。
如果某个社会不会遭到我所描述的那些反驳,那么它的收入不平等会有多大呢?这里的答案取决于这些经验事实,即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其他替代方式来组织经济。我自己的猜测是,这种不平等不会非常大:它一定远远小于美国20世纪中叶的那种不平等,更不用说自那时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了。
[1] 数据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和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s with 2014 Preliminary Estimates)”。访问网址为:Inequality.org。
[2]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298-300.
[3] 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 “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 2.
[4] Mishel and Davis, “Top CEOs,” 1-2.
[5] A Theory of Justice , section 4, 2nd edn, 15-16.
[6] 对此的详细阐述,参见A Theory of Justice , in chapter 3。
[7] 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72. 罗尔斯还要求,那些带有特殊益处的职位应当“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向所有人开放”,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详细地讨论了这项要求。
[8] 我感谢乔舒亚·科恩就这个问题与我进行了非常有益的交流。
[9] 罗尔斯写道:“差别原则并没有指定任何明确的范围并要求较多受益者和较少受益者的份额比例应当落到这个范围之内。”(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 68.)皮凯蒂也写道:“我想要强调这一点:关键问题是对不平等的证成,而不是不平等的程度本身。”(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264.)
[10] 在这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我并不同意科恩的这个观点:如果不平等不是来自收入较少者的选择,那么这些不平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并且这一点与那些产生这些不平等的制度所具有的特征无关。根据我已经陈述的观点,收入不平等是否正义取决于那些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和其他替代性政策所产生的后果。我认为,这一点与科恩的这个观点并没有不一致:(根本的)正义原则对事实是不敏感的(fact-insensitive)。(参见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 chapter 6.)我会同意我已经陈述的这个原则,即不平等是否正义取决于与后果有关的这些事实,它本身对事实是不敏感的。(尽管作为一个契约论者,我会认为其他一些根本的道德原则对事实是敏感的。)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我和科恩之间更基本的分歧可能是,哪个对事实不敏感的原则是正确的[以及由此导致了另一个分歧:关于正义的非根本的(non-fundamental)结论能够合理地依赖于哪种事实]。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本章的脚注20。
[11] 在确定某个基本结构是否得到证成时,哪些人的理由必须纳入考虑之中呢?答案是:所有被这个基本结构的要求所管辖的人,以及由它所提供的条件和机会来决定其生活前景的那些人。简而言之,如果这个基本结构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城镇里唯一的游戏”(按照布坎南的说法),那么这些人都将被包含在内。(关于布坎南的说法,参见“Rules for a Fair Game: Contractarian Note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130。)这包括那些通过担任各种经济职位而获得收入的人,例如工人、管理人员或股东。它还包括那些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无偿工作的人,例如有些人承担着照顾他人的工作。儿童、残疾的成年人或超过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自然而然被包含在内,因为他们并不代表着独立的人群。恰恰相反,童年和老年是每个正常人的不同人生阶段。所以每个人都有理由想要在童年时获得关爱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在老年时得到照顾,而处于残疾之中则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此外,这些人的理由也应当被纳入考虑之中,即那些选择不在社会中担任任何生产职务的人,例如范·帕里斯所设想的马里布的冲浪者(参见“Why Surfers Should Be Fed: The Liberal Case for an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这些人以这种方式被包含在内,这一事实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如果他们选择不去工作,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为他们提供基本收入或其他公共福利。要回应他们的理由,这可能只要求他们能够通过选择参与工作来获得收入,以及要求他们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来做出这种选择。(参见第五章中对“意愿”的讨论。)最后的这个条件解释了为什么让参与工作的意愿成为获取公共福利的条件,这对于冲浪者而言可能是正义的,但对于那些在不正义的条件下(例如美国的黑人贫民区)成长的人而言则并非如此。(参见Tommie Shelby, Dark Ghettos , chapter 6。)
[12] “Spreading the Wealth Around: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Joe the Plumber,” 295.
[13] 诺齐克提出了这种指责,并错误地把它当作一种针对罗尔斯的批评。参见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149-50。
[14] 这是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提出的观点:“任何消费工具的分配都只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的结果。”(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 531.)当罗尔斯强调他所提议的并不是一种“配置正义”(allocative justice)的标准时,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A Theory of Justice, 56 and 77, 和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 50-2。
[15] 这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补偿”(Kaldor-Hicks compensation)。参见J. R. Hicks, “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 49 (1939), 696-712; 和Nicholas Kaldor, “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Economics Journal, 49 (1939), 549-52。
[16] 我在第七章中所捍卫的那种个人自由。
[17] A Theory of Justice , section 12. 这可以被看成是平等关切的一种更高层次(higher-level)的版本:这个“更高的层次”所适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政府政策。
[18] A Theory of Justice , 2nd edn, 68.
[19]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330-1.
[20] Bivens and Mishel, “The Pa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s Evidence of Rents in Top 1 Percent Incomes,” 63. 鉴于这些职位本来就是令人向往的,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追求这些职位,即便没有巨额的金钱奖励作为激励。因此,如果某项政策始终坚持不提供这种奖励,那么它几乎不可能会导致无法产生出足够多的合格申请者。鉴于这一事实,按照我提供的那种解释,提供高额报酬的政策就会是得不到证成的。因此,屈服于G. A. 科恩在《从哪里采取行动》(“Where the Action is”)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富人的要求,这是不正义的。我并不认为这一结论对相关事实(关于有才能的人会如何回应一项始终不提供奖励的政策)的依赖是有问题的。不过科恩可能会不同意。
[21]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315-21.
[22]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参见Bivens and Mishel, “Pa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64。关关于高管薪酬的上涨可能会有哪些解释,也可参见Lucian Bebchuk and Yaniv Grinstei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
[23] 参见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509-10, 和Atkinson, Inequality:What is to be Done? , 186。
[24] 按照布鲁斯·韦斯顿(Bruce Western)和杰克·罗森菲尔德(Jake Rosenfeld)的评估,1973年至2007年之间,1/5~1/3的收入不平等加剧是由工会衰落造成的。参见“Unions, Norms,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一个地区工会的壮大与该地区没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工资增长有关。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将劳动力市场维持成一种社会机构,并且在这个机构之中,公平的规范塑造着工会部门以外的工资分配”(第533页)。我感谢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提醒我注意他们的工作。
[25]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各种市场中公司数量的减少,从而减少了对工人的竞争,而这会降低工人的议价能力,并因此降低他们的工资。参见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olicy Brief 2016,“Labor Market Monopsony: Trend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Responses”。这一点需要通过反垄断的政策来解决。
[26] 参见Piketty, Saez, and Zucman, “Distributional and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27] 阿特金森讨论过以这种方式来使用主权财富基金,参见Inequality , 176-8。他还指出,前一种策略(即增加工人的股份所有权)的一个成本是,那些充当中介的金融服务公司将抽走一部分利润(第161页)。
[28] 正如费希金所论证的那样。参见Bottlenecks , 220ff. and elsewhere。
[29] 对此的一些提议,参见Atkinson, Inequality , 132 and 237-9。
[30] 对此的一个综述,参见the Roosevelt Institute report, “Defining Financialization”。
[31] 正如墨菲和内格尔所提议的那样。参见The Myth of Ownership , 159-61。
[32]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chapter 15.
[33] 阿特金森强调过这个区分,参见Inequality , 95。
[34] 之所以是“某种非常类似的东西”,部分原因是:我允许把我们对自由的一般考量(以我已经确定的那两种形式)当作支持或反对基本结构的特征的理由之一,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所适用的那些基本社会益品只包含了某些“基本自由”。但这种差异会因以下这个事实而缩小:这些基本自由包含了诸如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等重要的个人自由。参见Freeman, “Capitalism in the Classical and High Liberal Traditions,”31, and n. 27, and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53, 54。
这本书所阐述的平等观既是关系性的,也是多元论的(pluralistic)。我坚持认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并且这些理由依赖于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不平等。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详细地考察了其中的一些反驳:对违反平等关切的反驳(第二章)、对地位不平等的反驳(第三章)、对干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反驳(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对造成巨大结果差距的经济制度的反驳(第九章)。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论述由这些分析所得出的某些一般性的结论。
这种多元论观点的一个优点是,它承认各种不平等形式之间的差异。除了超级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之外,现实中还有过着舒适小康生活的人和赤贫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种族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我们应当反对的,但我们之所以反对它们却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都违反了这个单一的要求——个人的前景应当是平等的。
我在第九章中讨论过某种经济生产力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这种分配会造成超级富豪和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它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平等地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
种族不平等则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经济机会的缺乏、教育和其他重要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供应,以及由法律制度施加的不平等对待。它还涉及一些人被剥夺了那些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有效手段的途径,包括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会被剥夺投票权。性别不平等同样也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以及缺乏平等的经济机会,这既因为在就业招聘和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着歧视,也因为家庭生活负担的不平等分配。它还涉及那种导致女性无法获得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的歧视,并且这种歧视一直都在维持着性别不平等。
赤贫的人由于无法接受教育而缺乏经济机会,并且他们也无法充分获得诸如医疗保健等其他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部分原因是穷人的利益在政治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穷人对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缺乏控制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会受到其他人的控制,而且他们几乎无法选择职业,并且还遭受着慈继伟所说的“能动性贫困”和“地位贫困”。
虽然我所讨论的大多数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例子都涉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平等观点只适用于这种情况,而不适用于全球不平等。我的探究是为了确定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的道德依据。我们从以下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反驳在依据上的不同蕴含着它们的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
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基于平等关切的反驳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或机构有义务提供某些好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国家机构,甚至是更地方性的机构,但相同的平等关切要求也适用于现有的国际机构。就机会平等而言,我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种制度性的理由会支持某项程序公平的要求,但这项要求并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拒绝来自其他国家的更合格的候选人,就跟拒绝具有类似资格的当地候选人一样,都是对程序公平的侵犯。但另一方面,实质机会的要求包含了应当为个人发展才能提供教育和其他条件的义务。我已经假定,这种义务由地方机构来承担,但我们可以论证道,它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基于不平等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影响而对不平等提出反驳,这种反驳关注的是不平等对某些特定政治制度的影响。但这种反驳可以应用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那些依赖某个国家的法律而生存的大公司,它们可能会干扰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的公正性。同样地,如果对不平等的反驳是基于它会让某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控制权,那么这种反驳就能适用于任何存在着这种控制权的地方。最后,我在第九章中讨论的那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是因为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无法得到证成,这包含了全球不平等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这些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会互相重叠。如果基本结构的某些特征会产生无法得到证成的结果不平等,那么除了最富裕的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有理由来反对这些特征。同样地,所有无法平等地获取政治影响力的人都有理由来反对会产生这种影响的经济不平等。
而如果一些人没有被提供充足的重要公共福利(例如教育),那么他们会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这一点。这种反驳首先是一种针对不充足(insufficiency)的反驳,而不是一种针对不平等的反驳;但只要这种不充足是由人们无法获取政治影响力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政府违反平等的关切,那么这种反驳就变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反驳。不只是赤贫的人,那些收入位于中间五分之一的人也会持有这些反驳。但穷人的反驳会更加强有力,因为他们享受的服务水平甚至会更低。除了这些反驳之外,穷人也有理由来反对他们的不平等地位,而那些遭受各种歧视的人也会持有这种理由,并且他们的理由甚至更加强有力。
这些反对不平等的重叠理由会产生这种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即那些过得最差的人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优先权。如果某些不平等的形式会影响到穷人,尤其是影响到那些既贫穷又受到歧视的人,那么我们便有最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这些不平等的形式,并且尽可能地消除它们。但这并没有使得我所提出的观点变成了一种优先主义的观点并且与平等主义的观点相对立 。这是因为支持这种优先权的大部分理由——尤其是对地位不平等、违反平等关切和政治与经济制度缺乏公正性的反驳——本身都有平等主义的特征。它们至少在广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反对在一些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就刚才提及的那些理由而言,例如地位不平等和违反平等关切,这些理由在狭义上也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建立在特定的平等形式的价值之上。
不要夸大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制度(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继续体现着种族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歧视,而且还继续体现着其他形式的程序不公平。此外,我们还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实质机会的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便机会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也不会导致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机会平等预设 了某些对不平等职位的其他证成,而它并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证成。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都很重要,即便它们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它们也非常值得追求。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恰当地理解这些价值,尤其是理解能力、优点、努力和选择这些观念,因为人们经常使用这些观念来表述这些价值。
恰当地理解能力、努力和选择的道德意义使我们能够避免道德主义和错误的应得观念。我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已经尝试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与正义问题相关的那种能力既依赖于制度职务的结构,也依赖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现有发展条件。因此,如果我们独立于任何制度来定义个人属性,那么能力并不是一种正义的制度所应当奖励的个人属性。而选择和努力之所以与证成不平等相关,是因为下述这个事实能够破坏人们针对他们缺乏某些优势所提出的反驳:如果他们之前选择付出必要的努力,那么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这些优势。但是,一个人有机会去选择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一事实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才能够具有这种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效果,即这个人在拥有那个选择的机会时,他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
在前面的章节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是:一个社会是否展现出理想的平等形式,或者是否展现出应被反对的不平等形式,这将依赖于那个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在第三章关于地位的讨论中,这种依赖以好几种方式体现出来。许多歧视形式都涉及人们对于某些诸如肤色等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存在着基本的评价错误。而贫穷是否涉及缺乏地位也依赖于某个社会普遍流行的评价态度。此外,一种完全任人唯才的制度会是一种应被反对的等级制,这种观点依赖于这个(可信的)假设,即这个社会的成员会过度重视这种制度所奖励的那些成就。
这对我们关于机会平等的思考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境。实质机会要求人们的成长环境要让他们看到,那些使他们有资格获得优势职位的能力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值得奋斗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鼓励人们过度重视这些特定形式的成就和成功,那么它可能会遭到反对。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同意罗尔斯(以及诺齐克和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即不存在任何有效的一般原则可以用来详细指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应当采取的模式。收入和财富的某种分配是否正义,这取决于产生这种分配的制度的性质;如果产生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制度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获得证成,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公平的。对这些制度的证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依赖于这些经验事实: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各种经济和政治安排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像这样一本书的任务则是,试图在这种证成中确定与此相关的规范性要素。
关于这一点,我既有否定性的主张,也有肯定性的主张。我的否定性主张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经济制度无法通过诉诸某些独立的财产权概念或应得概念来获得证成。而我在第九章中提出的肯定性主张则是,这种证成因此必须诉诸人们基于这些制度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而接受这些制度的理由。除非避免收入不平等会侵犯重要的个人自由,或者会干扰生产过程并导致那些拥有较少收入的人过得更糟糕,否则产生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无法获得证成的。这种证成性的标准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更弱,因为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会让那些过得差的人尽可能地过得好,此时不平等才是正义的。但是,这个较弱的原则却足以解释为什么盛行于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应当受到反对。此外,得出这一较弱原则的那个论证思路也会为罗尔斯的较强版本提供支持。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人们接受或反对制度的理由包含了他们在个人自由这方面上的利益。这些理由包括:人们既有理由想要机会变得可被利用,也有理由想要在对这些选项做出选择时处于良好的条件之下,并且还有理由反对受到他人的控制。对制度的证成需要把每个人拥有的这类理由都纳入考虑之中,包括权利在被强制执行时所针对的那些人以及权利的持有者。
人们拥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这些理由分别基于不平等的影响、它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产生它的制度。这些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非都来源于某种单一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它们在以下这个过程中所共同扮演的角色: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社会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通过这个过程而获得证成。因此,我的观点在两个层面上属于平等主义的观点。在抽象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主张,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以一种认真对待他们所有的利益并给予这些利益同等重视的方式来获得证成。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承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受到某些特定方式的不平等对待。这些正是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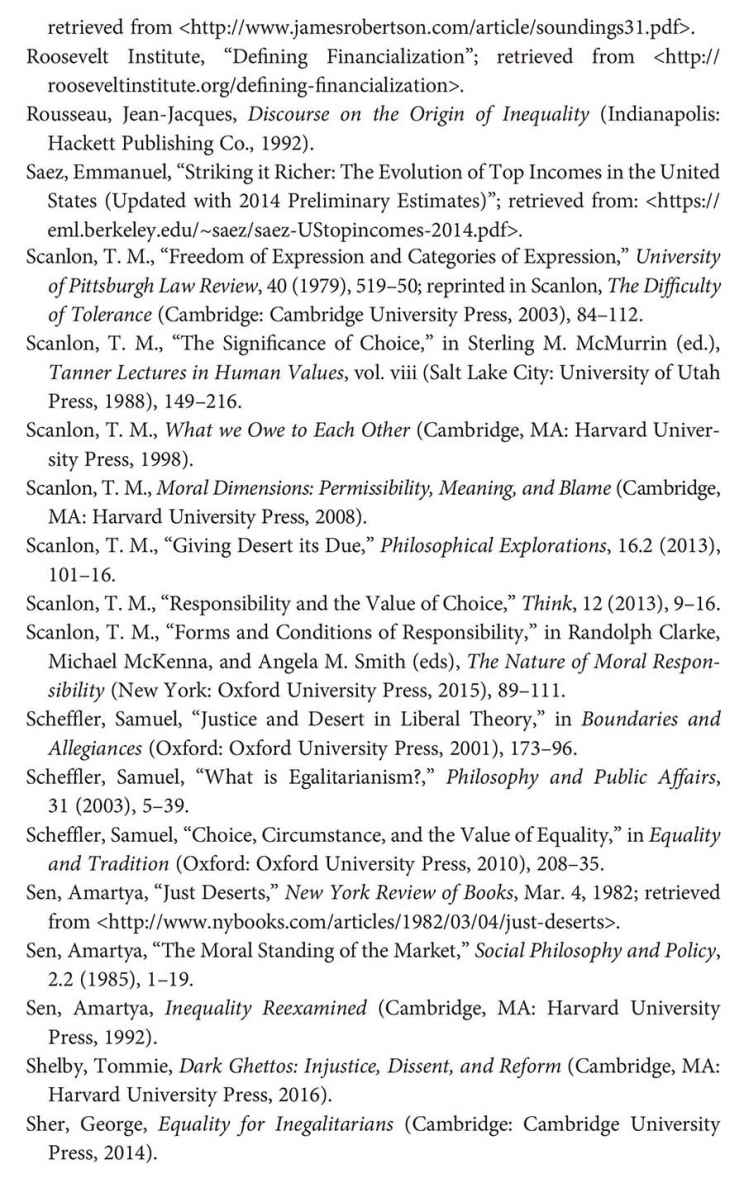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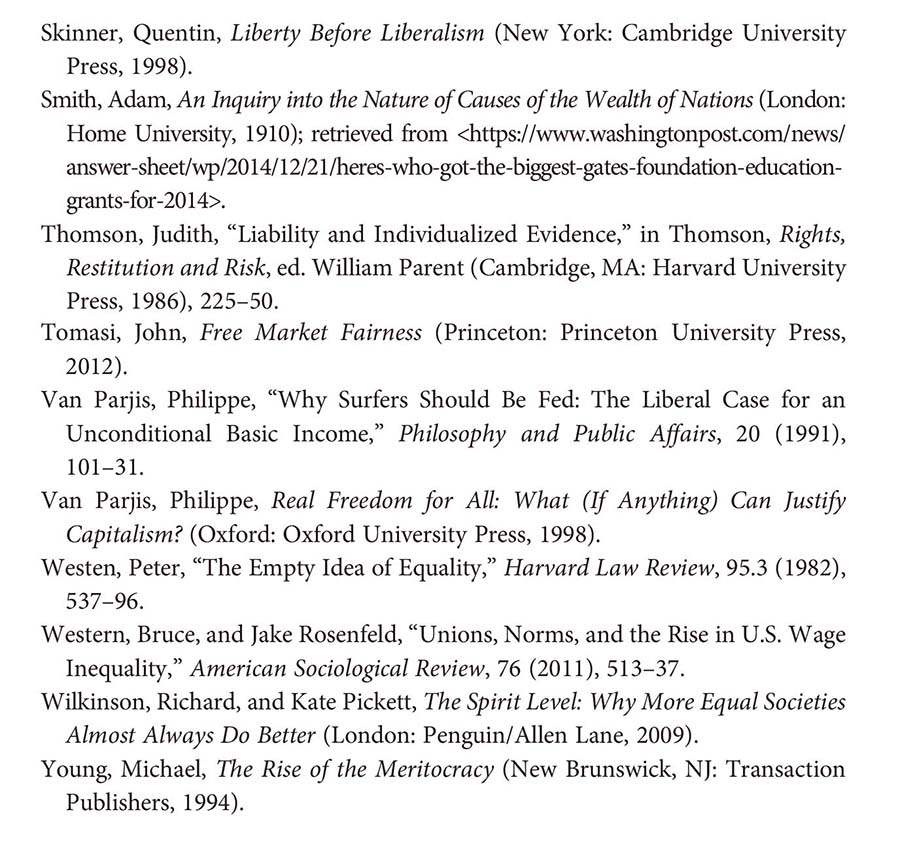
本书的主要框架来自托马斯·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篇讲稿在2003年的时候又被斯坎伦收入《宽容之难》这本论文集中。自林德利讲座之后,斯坎伦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新的内容,并且以《平等何时重要?》为题多处发表演讲。这些内容经扩充和打磨后,最终形成了当下这本书。所以,实际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斯坎伦关于平等的论述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这两本书中,约翰·罗尔斯在讨论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时,就基本沿用了斯坎伦所提出来的框架。此外,关系平等主义(又称“社会平等主义”)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兴起也和斯坎伦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斯坎伦正是关系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书中,斯坎伦把自己的平等观概括为“多元论的”和“关系性的”,前者意指我们有多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后者则指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应当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斯坎伦重点讨论了六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它们分别是:(1)不平等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2)不平等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3)不平等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4)不平等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5)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6)当下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在本书中针对不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给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许多师友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在此我想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先,如果不是张容南老师帮我联系出版方并主动提出担任审校人,我恐怕没有机会接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此外,张老师不仅对我的译稿提出了非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而且还针对很多翻译细节和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无疑使这本译作的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我十分感谢张老师对此的付出,以及对我的指导和支持。
在我充分吸收了张容南老师的建议后,我的同窗好友兰超又主动帮我把这本译作的前五章进行了一次校对,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改善意见。我感谢兰超的无私付出以及对我的译文的肯定。最后,针对本书部分术语和句子的翻译,我还向葛四友、郭昊航、林秀妮、马晨和田洁等师友请教过,我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和我进行讨论,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指导。我尤其想对葛四友老师表达特别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支持和鼓励。
尽管对于我的第一本译著,我已经竭尽全力地改善它的译文质量,但限于时间和能力,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批评赐教。我的联系邮箱是:lupengjie@ruc.edu.cn。
陆鹏杰
2019年5月,人大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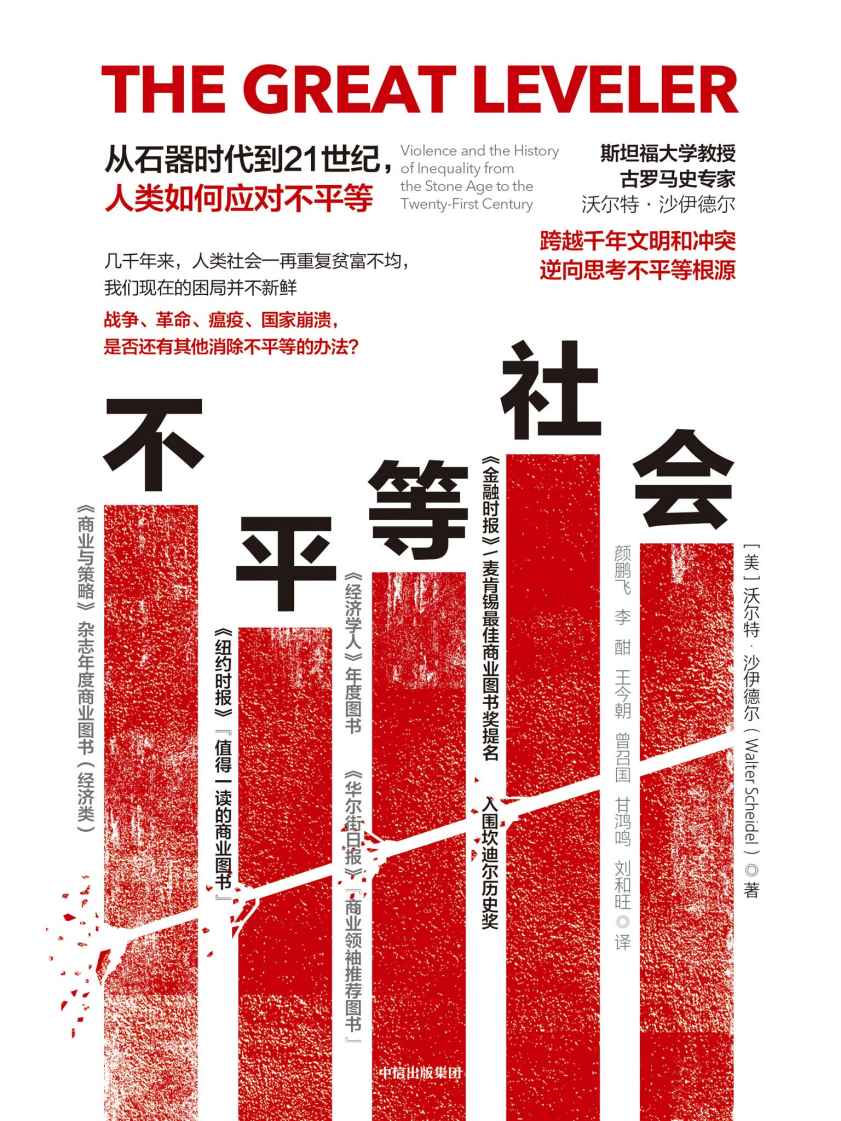
“从享用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分给穷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应得的一份吧。”
——莎士比亚,《李尔王》
“杀死富人,就不会再有穷人。”
——《论财富》
“上帝多么经常地发现,治疗对我们来说,比危险本身更糟糕!”
——塞涅卡,《美狄亚》
献给我的母亲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1]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在欧洲和北美、前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财富分布都变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 [2]
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即使如此,美国面对中国也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相当小,但有更大数量的财富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 [3]
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一本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长达700页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个月内卖出150万本,并且跃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畅销书榜榜首。在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党内初选当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于“富豪阶层”的无情谴责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给予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助。中国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们全部的疑虑,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是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们能够追踪公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程度(图I.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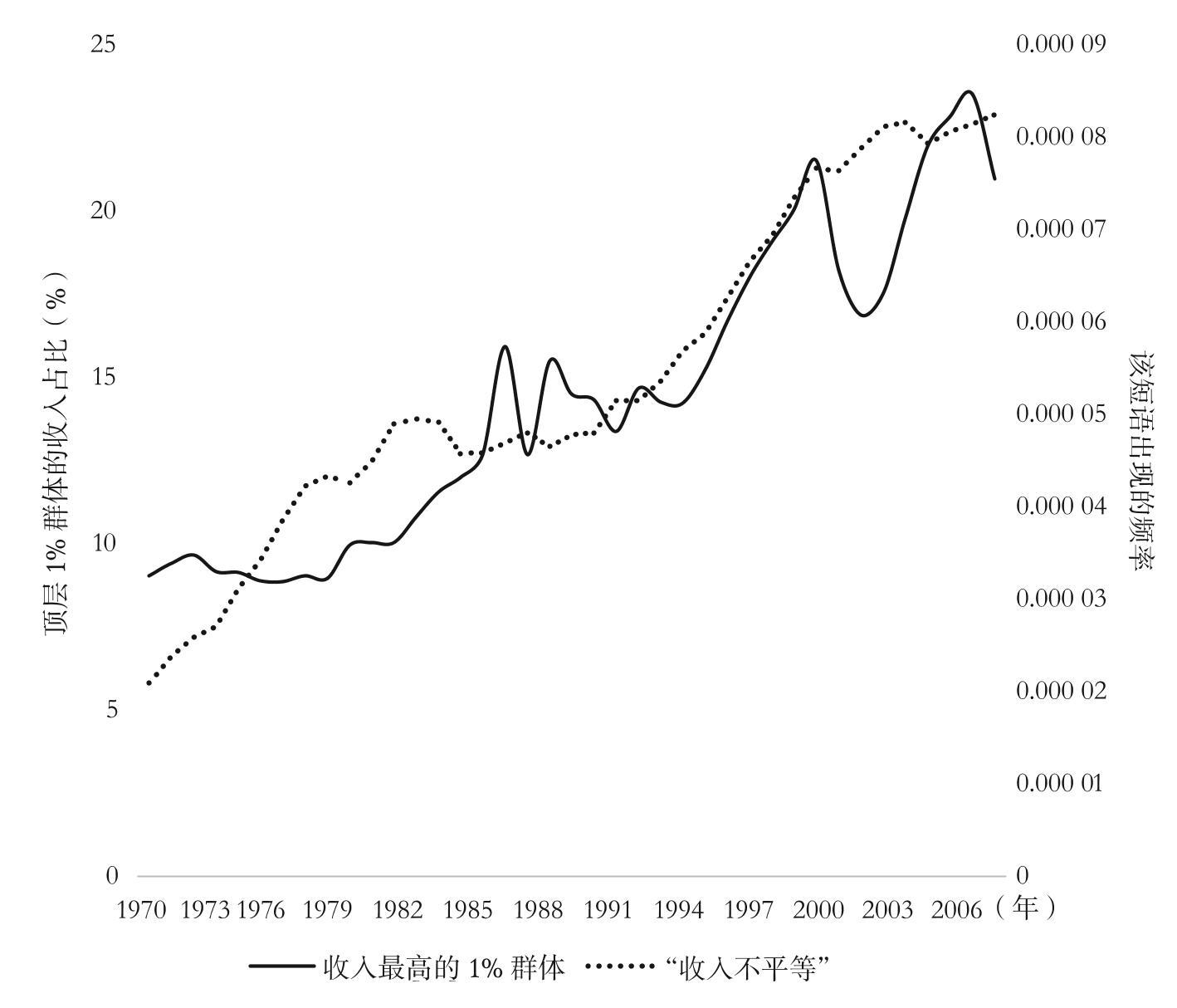
图I.1 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每年)与“收入不平等”这一短语的援引情况(3年移动平均值),1970—2008年
所以,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5]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物质上的不平等要求获得超出我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上万年前,剩余就已经存在了,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追溯到上一个冰期,狩猎–采集者发觉埋葬一些人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使用的方式更铺张。但正是食品的生产,即农业和畜牧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出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性成为全新世的一个主要特征。动植物的驯化使得积累和保存生产资源成为可能。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了这些资产的权利范围,其中包括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各种各样的实践的影响:健康、婚姻策略和繁殖成功、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丰收以及蝗灾和牛瘟决定了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多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和努力的后果会带来长期的不平等结果。
原则上,可以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这些干预机制使得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就像一些前现代社会已经做到的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的进化通常会出现相反的效应。食物来源的驯化同样影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竞争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和强制力量,扭曲了收入和财富的获取。这使得政治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在农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富裕:腐败、勒索、抢劫往往使得从对公共服务进行支付和捐赠中获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因此,许多前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在较低的人均产出和最小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少数精英阶层已经探索了剩余占有的极限。当更多的良性制度促进了更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兴的西方世界,它们继续维持着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业化、金融部门创新、贸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资本持有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活动租金的下降,精英阶层财富的传统来源被扼杀了,更为安全的产权和国家承诺加强了对世袭私人财富的保护。尽管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
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就像他们在《圣经》中的同行一样,他们“从地上夺走了和平”,并且“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有时他们单独行动,有时相互配合,他们产生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无异于天启。数亿人在他们的身后死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时甚至急剧缩小了。 [6]
只有特定类型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大多数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影响,虽然古代冲突形式充斥着征服和掠夺,很可能使得获胜的精英阶层一方变得富有,使得失败的一方变得穷困,但不那么清晰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可预见的后果。为了使战争能够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需要贯穿整个社会,在通常只有民族国家才可行的规模水平上动员人民和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矫正力量。工业性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展、工会化和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拿破仑时代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产生了具有混合分布特征的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相关的证据就越少。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早的例子,说明军事动员和平等制度的激烈程度如何有助于抑制物质不平等,尽管结果不一。
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二种主要的矫正力量,即变革性的革命。内部冲突通常不会减少不平等:农民运动和城市起义在近代历史上很常见,但通常是失败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往往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如果想要重构物质资源的获取途径,需要格外激烈的暴力性的社会重组。与具有矫正作用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类似,这也主要发生在20世纪。采取没收、重新分配等手段,然后常常实施了集体化政策的党派,戏剧性地矫正了不平等。这些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是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暴力,最终以大量的伤亡人数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流血较少的社会改革运动,则在相对较小规模上起到了矫正作用。
暴力可能会彻底摧毁国家。国家灭亡或者系统崩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矫正方式。对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富人要么处于或接近政治权力阶层的顶端,要么与那些有权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各国为维持超过生存水平之外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不论以现代标准来看它显得如何勉强。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地位、关联和保护都会受到压力或者完全丧失。虽然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遭遇损失,但富人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精英收入和财富的下降或崩溃压缩了资源的总体分布。只要有国家存在,这些状况就会发生。最早已知的例子可以回溯到4000年前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帝国。即使在今天,在索马里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一度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塑现存的政治制度实现再分配和再平衡,而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把此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了。前三名骑士代表了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按照先后次序出现(最大的革命是由最大的战争引发的,国家崩溃通常不需要同样的强大压力),因而只需要足够的强度。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得他们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
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
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
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在种族和民族方面,在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和机遇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准确。然而,像“暴力性冲击和从石器时代到现在及以后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全球历史”这样的英文副书名,不仅会使出版商失去耐心,而且也会被读者排斥。毕竟,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一个更详细的标题将会立刻显得更加准确,同时过于狭隘。
关于经济不平等,我并没有试图去论及各个方面。我所聚焦的是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且得到很多讨论的主题。我考虑特定社会中的情况,没有明确指向那些刚才提到的许多其他不平等的来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长期追踪和比较这些因素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我主要想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的问题,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宽泛地说,在我们人类接受食物生产及其导致的一般性必然结果,定居生活和形成国家,并且承认某种形式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之后,关于物质不平等的向上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压力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我们可能粗暴地标识为胁迫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将需要对更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单独研究。 [7]
最后,我讨论了暴力冲击(以及替代机制)和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是否(以及假设如此,那么是如何)由不平等促成了这些剧烈的冲击。我不愿意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由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是历史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不容易解释关于那种外部环境下的具体冲击。在有着可比较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现代社会当中,内部稳定性变化很大。一些经历过暴力性关系破裂的社会并非特别不平等。某些冲击主要或完全是外生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平衡矫正了不平等的传染病大流行。甚至人类造成的事件,如世界大战,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些没有被直接卷入这些冲突之中的社会。关于收入不平等在加速内战爆发中的作用的研究凸显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不应该用来表明,国内资源不平等不可能促成战争和革命的爆发或国家崩溃。这仅仅意味着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确定总体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暴力冲击的发生之间有系统性的因果联系。正如最近的研究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对具有一种分布维度的更具体特征的分析,例如分析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在解释暴力冲突和国家崩溃之间的关系上更有前景。
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将暴力冲击视为对物质不平等产生影响的一种离散性现象。设计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评估作为矫正力量的这种具有长期冲击性的影响力,而不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认这些事件与先前的不平等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如果我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因果关系的单一箭头方向上,即从冲击到不平等,会鼓励人们从事反向关系的进一步研究,那就更好了。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将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可观察到的变动内化。即便如此,不平等和暴力冲击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循环肯定值得深入探讨。我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8]
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它可以表示为分数或百分数,我更喜欢前者,以便更好地将其与收入或者财富比例分辨开来,后者一般是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的。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下文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每当我使用“收入不平等”这个术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我指的就是前者。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此外,在现代西方建立广泛的财政再分配制度之前,市场、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差异一般都很小,这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一样的。在这本书中,收入份额总是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基础。关于收入份额的当代和历史数据,特别是分配比例最顶层群体的那些数据,通常源于财政手段干预前的收入的税收记录。在个别地方,我也谈到了不同比例或者收入分配特定的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相对权重的替代性测度。虽然存在更复杂的不平等指数,但其通常不适用于那些需要交叉使用高度多样化数据集合的长期研究。 [9]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在这本书中,我遵循惯例,优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等这些相对不平等的标准测度,但在适当的时候会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10]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本书结束部分的附录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它。 [11]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调查往往缺乏必要的质量以支持可靠的国家层面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宽的置信区间不仅会阻碍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会使得跟踪调查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加困难。衡量财富整体分配的努力甚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多的精英资产被认为藏匿在海外,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数据丰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收入份额通常是从税收记录中计算出来的,其质量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差别很大,而且容易受到逃税动机的扭曲。低收入国家的低参与率和政治驱动的应税收入定义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中,越来越多的关于最高收入份额的信息得到汇编和在线出版,使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理解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并将注意力从例如基尼系数这样有些不透明的单值测度转移到更为明确的资源集中度指数上了。 [12]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13]
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不直接记录分配状况的替代性数据,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土地租金与工资的比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当中,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最重要的资本类型价值的变动,能够反映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相对收益的变动:上升的指标表明,地主的繁荣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即人均GDP与工资的比率也是如此。GDP中的非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一指数就越高,收入就可能越不平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对于特定的本地场所,租金和工资的报告是可信赖的,但并不一定对更大的群体或者整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任何前现代社会的GDP进行猜测,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大的误差。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实际收入是一个能够更广泛获取,但缺少一些启发意义的代理指标。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谷物等价物表示的实际工资现在已经追溯到4000年前,成为识别异常升高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实例,这是一种可能与不平等程度降低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那种不能通过参照资本价值或GDP数据做出必要调整的实际工资信息,对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说,依然是一个粗糙的、不甚可靠的指标。 [14]
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前现代社会税收记载研究,以及对于实际工资、租金与工资比率,甚至是GDP水平的重构的可观进展。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在20年,甚至是10年以前,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是最有希望的不平等标志——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唯一的。当精英阶层在住房、饮食或者是墓葬等方面奢华消费的考古证据让位给更为适度的遗物或者社会分层的迹象完全消失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在传统社会中,富人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往往是仅有的控制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从而可以承受重大损失的人,这些损失在有形的记录中是可见的。人类身高和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化也同样与资源的分布有关,尽管其他因素,如病原体负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越是远离以更直接的方式记录不平等的数据,我们的理解就注定会变得更具推测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扩展,否则描述这种全球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就试图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文档资料上的一个巨大的梯度,即从有关美国近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详细统计数字到文明的曙光中隐约存在着资源失衡的迹象,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数据集。所有这一切以一种合理连贯的分析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不小的范围内,这是这个导言标题中所援引的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我选择用我自己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组合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紧接着的这部分内容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不平等的演变,因此章节顺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1~3章)。
这一情况,在我们转向四骑士——暴力矫正的4种主要驱动力量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一四重奏组合的前两个成员,即战争和革命的部分时,我的观察分析开始于20世纪,随即返回历史当中。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大规模动员战争和改造性的革命为手段的矫正,主要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不仅产生了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而且以范例的形式代表并确实构成了它(第4~5章)。第二步,我寻找这些暴力性破坏的来路,从美国内战一直追溯到古代中国、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近代时期的无数次起义(第6~8章)。我在第6章最后部分讨论内战的时候依循了同样的轨迹,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冲突的结果一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结束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在探讨它们是否能被应用到更遥远的过去之前,在现代数据基础上建立根基牢固的暴力矫正模型。
在第五部分对瘟疫的分析当中,我从得到的有记录的例子——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第10章)逐渐转向更少为人所知的例子,从而使用了相同策略的一个修改后的版本,这些例子的其中一个(1492年后的美洲)正好更接近近期,其他则位于更古老的时代(第11章)。其原理是相同的:在我寻找其他地方类似事件之前,在现有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流行病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暴力性矫正的关键机制。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灭亡和制度崩溃,我对这一组织原则进行了逻辑总结。在分析大体上局限于前现代历史的现象之时,年代学几乎不重要,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定案例的日期比证据的性质和现代学术规范更不重要,后两者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差异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因此,在我转向讨论其他我不太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前,我先举了几个得到很好验证的例子(第9章)。第六部分,关于暴力性矫正的替代方案,大部分是按主题排列的,因为我在转向反事实结果(第14章)之前评估了不同的因素(第12~13章)。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一起形成了我的专题性分析,又回到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格式,从最近的不平等复苏(第15章)转到相邻或者更遥远未来的矫正作用的前景(第16章),这就完成了我整个的演化性概览。
作为一项汇集了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低地玛雅人和当今的索马里的研究,这可能令我的历史学家同行困惑不解,但我希望对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困扰会少一些。正如我之前所说,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想找出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矫正性力量,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弥合学科内外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鸿沟,并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难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动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尝试呢?对这个疑问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决两个单独但相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今天重要吗?为什么它的历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论瞎扯》(On Bullshit )的研究,他通过在序言开始部分对引用的奥巴马的评价进行反驳而开启了他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 ):“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不是美国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实际上是我们太多的人民‘贫穷’。”毫无疑问,贫穷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在美国被视为穷人的人在中非看来却并不如此。有时贫穷甚至被定义为不平等的一个函数(在英国,官方贫困线被设定为收入中值的一个比例),尽管绝对标准更为常见,例如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价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门槛值,或者是参考美国的“一篮子消费品”的成本。没有人会否认,不管如何定义贫穷,它都不是受人欢迎的,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证明“这样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生活有负面影响,而不是证明可能与之相关的贫穷或巨大财富。 [15]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一再指出,很难对这种关系进行评估,而且问题的理论复杂性并不总是与现有研究的经验规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确实与低增长率有关。例如,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经济增长更快,而且导致增长期更长。不平等似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这一备受争议的命题,即美国家庭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进了信贷泡沫,从而促发了2008年的大萧条,因为低收入家庭利用现成的信贷(部分是由上层人士的财富积累产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体的消费模式。相比之下,在更严格的贷款条件下,财富不平等被认为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16]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17]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18]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19]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建议者往往对这一历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确评估。那样是应该的吗?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农业和非民主的基础,以至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体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证明,那些用来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在过去完成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问,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个大矫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来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答案。
[1] Hardoon, Ayele, and Fuentes-Nieva 2016: 2; Fuentes-Nieva and Galasso 2014: 2.
[2] Global wealth: Credit Suisse 2015: 11.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比重数据来自WWID:最高的0.01%、0.1%和1%的比重,如果包含资本所得,将会从1975年的0.85%、2.56%和8.87%上升到2014年的4.89%、10.26%和21.24%,这意味着该数字分别获得了475%、301%和139%的增长,以及在最高0.1%和最高1%收入群体之间有74%的增长。
[3] 在2016年2月,比尔·盖茨的财富达到了754亿美元,大约等于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100万倍和中位数水平的140万倍。在1982年发布的《福布斯》的400强排名中,丹尼尔·路德维格的资产为20亿美元,位列第一,分别相当于那时美国家庭年收入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的5万倍和8.5万倍。至于中国的亿万富翁的数据,参见: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676814-crackdown-corruption-has-spread-anxiety-among-chinasbusiness-elite-robber-barons-beware。
[4]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Economic Mobility,” December 4,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2/04/remarks-president-economic-mobility.Buffett 2011.Bestseller:Piketty 2014.China: State Council 2013.Fig.I.1: WWID (including capital gains); 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这一热门话题的重要性在最近由于一套有着《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样时髦标题诗集的出版而得到了强调(Seidel 2016)。
[5] U.S.: WWID, and herein, chapter 15, p.409.England: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79 table 7.A4.For Rome, see herein, chapter 2, p.78 (fortunes), chapter 9, p.266 (handouts),and Scheidel and Friesen 2009: 73–74, 86–87 (GDP and income Gini coefficient).For overall levels of inequality, see herein, appendix, p.455.For the Black Death, see herein,chapter 10, pp.300–306.
[6] Revelation 6:4, 8.
[7] Milanovic 2005;2012; Lakner and Milanovic 2013;Milanovic 2016: 10–45, 118–176是关于国际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研究。Anand and Segal 2015综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Ponthieux and Meurs 2015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上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工作的全面概述。也可以参考Sandmo 2015关于经济思想中的收入分配的分析。
[8] For more on this issue, see herein, chapter 14, pp.392–394.
[9] 尽管人们常常这样讲,但基尼系数G永远达不到1,因为G=1-1/n,其中n是人口规模的大小。参考Atkinson 2015: 29–33对于不同收入类型和相关指标的精辟总结,需要控制除了转移支付之外的公共服务的价值,以及应计和已实现损失之间的差异。基于这种大范围综合分析的目标,也可以放心地把这种差别放在一边。For ratios of income shares, see, most recently, Palma 2011 (top 10 percent/bottom 40 percent) and Cobham and Sumner 2014.For the methodology of inequality measurement, see Jenkins and Van Kerm 2009 and, in a more technical vein, Cowell and Flachaire 2015.
[10] See Atkinson and Brandolini 2004, esp.19 fig.4, and also Ravaillon 2014: 835 and herein,chapter 16, p.424.Milanovic 2016: 27–29 offers a defense of relative inequality measures.
[11] See herein, pp.445–456; for the example, see p.445.
[12]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nis and top income shares, see Leigh 2007; Alvaredo 2011;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83–687;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03–606,esp.504 fig.7.7.For Gini adjustments, see esp.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679, 681–683 and herein, chapter 15, p.409.Palma 2011: 105, Piketty 2014: 266–267,and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06 str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op income shares.For Gini comparisons, see, e.g., Bergh and Nilsson 2010: 492–493 and Ostry, Berg, and Tsangarides 2014: 12.两者都偏好《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集》中报告的基尼系数值,我在这本书从头至尾也在使用这一数据,除非我引用了其他学者的参考文献。Confidence intervals are visualized at the SWIID website, http://fsolt.org/swiid/;see also herein, chapter 13, pp.377–378.For the concealment of wealth, see Zucman 2015.Kopczuk 2015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of measuring U.S.wealth shares.For the nature and reliability of top income data, see esp.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479–491 and the very extensive technical discussions in the many contributions to Atkinson and Piketty 2007a and 2010.The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WWID)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wid.world/.
[13] All these and additional examples are discussed throughout Part I and in chapter 9, pp.267–269, and chapter 10, pp.306–310.
[14] Once again, I employ these approaches in much of this book, especially in Parts I and V.Evidence for real wages going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has been gathered at “The IISH list of datafiles of historical prices and wages”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http://www.iisg.nl/hpw/data.php.Scheidel 2010 covers the earliest evidence.For historical GDP data, estimates, and conjectures, see the “Maddison 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15] Frankfurt 2015: 3.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说,我很愿意承认所有的历史都是值得探索的,知识就是其自身的回报。然而再一次谈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有些问题可能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
[16] For the difficulties, see Bourguignon 2015: 139–140 and esp.Voitchovsky 2009: 569, who summarizes conflicting results (562 table 22.11).Studies that report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clude Easterly 2007; Cin gano 2014; and Ostry, Berg, and Tsangarides 2014, esp.16, 19(more and longer growth).最高分位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在接下来的5年中对增长率会产生影响:Dabla-Norris et al.2015。在1985—2005年间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使得OECD成员从1990—2010年间的累积增长减少了4.7%:OECD 2015: 59–100, esp.67.一项对104个国家的调查表明,1970—2010年间,收入不平等加剧倾向于提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以及人力资本),而对中等收入或者高收入者相反:Brueckner and Lederman 2015。这与先前的一项研究是一致的,这项研究表明其对发达经济体以外的经济增长无法造成负面影响:Malinen 2012。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通过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相对大小所表达的不平等,那么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仅限于与政治联系有关的财富不平等:Bagchi and Svejnar 2015。Van Treeck 2014回顾了关于不平等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的辩论。Wealth inequality and access to credit: Bowles 2012a: 34–72;Bourguignon 2015: 131–132.
[17] Björklund and Jäntti 2009 and Jäntti and Jenkins 2015 are the most recent surveys.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see Corak 2013: 82 fig.1 and Jäntti and Jenkins 2015: 889–890, esp.890 fig.10.13.OCED成员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和英国报告了高度不平等和低流动性,而北欧国家相反:OECD 2010: 181–198。Björklund and Jäntti 2009: 502–504发现,在美国,家庭背景对经济地位的影响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要大,尽管更广泛的跨国研究有时只显示出微弱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长大的男人,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不太可能经历过社会流动:Andrews and Leigh 2009; Bowles and Gintis 2002 (indicators); Autor 2014: 848 (self-perpetuation,education).Reardon and Bischoff 2011a and b discu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Kozol 2005 focuses on its consequences for schooling.See also Murray 2012 for a conservative perspective on this issue.撇开经济不平等的变化不谈,克拉克在201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从长远来看,社会流动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往往更为温和。
[18] For inequality and civil war, see hereafter, chapter 6, pp.202–203, and cf.briefly Bourguignon 2015: 133–134.Politics: Gilens 2012.Happiness: 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l 2009: 374, and see also Clark and D’Ambrosio 2015 on inequality’s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ttitudes.Health: Leigh, Jencks, and Smeeding 2009; O’Donnell,Van Doorslaer, and Van Ourti 2015.然而,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正在扩大:Bosworth, Burtless, and Zhang 2016: 62–69。
[19] Atkinson 2015: 11–14区分了为什么不平等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工具性原因和内在原因。也可以参考Frankfurt 2015。至于公平性,Bourguignon 2015: 163谨慎地将引号应用于“正常”的不平等水平的概念上,但在这些术语中定义了“前20或30年”的条件。
不平等总是伴随着我们吗?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非人类亲戚,即非洲的这些类人猿——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有着严密等级划分的生物。成年雄性大猩猩被划分为极少数拥有许多配偶的统治者和很多完全没有配偶的其他黑猩猩。银背大猩猩不仅支配着它们种群中的雌性,而且还支配着很多成年后依然留下来的雄性。黑猩猩,尤其是雄性,在争斗地位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恃强凌弱和富有攻击性的炫耀与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各种服从行为相匹配。在一个有50个或者100个成员的群体中,社会地位成为生活中核心且令人备感压力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占据了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但它们又总是在寻求进一步改善的路径。同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通过离开原有群体以摆脱专横的优势阶层的雄性,要面对的是被其他群体中的雄性杀戮的风险,因此它们将倾向于维持原状,加入竞争,或者臣服。与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界限相呼应,这种强大的约束使不平等状况加剧。
它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向世界展示的可能是一幅温和的图景,但是同样以拥有阿尔法雄性和阿尔法雌性,即雄性领袖和雌性领袖为特征。与黑猩猩相比,尽管倭黑猩猩较少使用暴力和欺凌,但它们仍维持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尽管隐蔽排卵和雄性对雌性系统性控制的缺乏,减少了针对交配机会的暴力性冲突,等级制度还是在雄性间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些物种当中,不平等表现在获取食物上的不均衡(与之相类似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以及最为重要的在繁殖上的成功。支配性的等级制度成为标准的模式,社群首领拥有标准的模式,即它由体型最大、体格最强壮和最有进取心的雄性组成,它们占有最多的消费资料和雌性。 [1]
这些共同特征,不太可能只是在它们共同的祖先分化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约1100万年前随着大猩猩的出现而发轫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300万年,随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与后来进化为南方古猿并最终成为人类的这一支相分离。即便如此,关于不平等的显著社会表现可能在灵长类动物中并不总是一致的。等级制度是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离我们更远一点的、更早分化出去的灵长类“亲戚”,现在则更不合群,它们或者自己独立生活,或者生活在非常小或临时的群体中。这对长臂猿和红毛猩猩来说也是如此,前者的祖先是大约2200万年前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后者最早是大约1700万年前从类人猿中形成的,现在红毛猩猩仅在亚洲生存。反过来,等级体系的社会性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一科所属的非洲属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意味着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已经表现出不同类型的这种特征,而更远一些的先祖并不一定如此。 [2]
对古人类和新人类中的不平等而言,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情况进行类推的指导意义不大。我们拥有的最好替代性证据,就是关于二型性的骨骼数据,即某一性别的成年成员(在这里是指雄性)在多大程度上比另一性别的成年成员更高、更重和更强壮。就像在海狮中一样,大猩猩中有或没有配偶的雄性个体之间,以及雄性和雌性个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均衡,这与较高程度的雄性偏向的二型性是相关联的。从化石记录中判断,新人类之前的古人类(可以追溯到超过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傍人)二型性比新人类更为突出。如果这种近年来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正统观点能够得到支撑,那么一些出现在400万—300万年前的最早物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和湖畔种,就应该由一个具有超过50%体重指数优势的雄性来领导,而后期的一些物种占据了它们和新人类之间的位置。随着200多万年前有着更大脑容量的直立人的出现,二型性已经下降到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观察到的一种相对适中的数量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二型性的不平等程度与普遍存在的、斗争性的男性间对女性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或者由女性的性选择所决定,那么减小的性别差异可能就是男性之间繁殖能力差异变得更小的信号。依此来看,进化减弱了男性之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即便如此,对男性来说,繁殖不平等率高于女性这一现象一直与一定水平的、以繁殖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相伴存在。 [3]
其他一些可能开始于200万年前的发展也被认为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大脑和生理机能的变化促进了合作繁殖及抚养,这一变化抵御了优势群体的侵犯,同时也缓和了更大群体中的等级差异。暴力的使用方式的创新也可能有助于这一进程。任何有助于低等级群体抵抗优势群体的东西都限制了后者,因此也降低了整体的不平等性。地位较低的雄性建立的联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使用投掷兵器是另一种方式。在封闭的场所战斗,无论是徒手还是使用牙齿,又或是用棍棒和石头,都对更强壮和更富侵略性的雄性有利。在武器能够在更长的距离上使用之后,它就开始扮演一种具有平衡性的角色了。
大约200万年前,肩部的结构变化首次使得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投掷石头或者其他物体变得可行了,这是一种早期物种和今天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的技能。这种调整不仅提高了打猎能力,同时也使得低等级群体对社群首领的挑战变得更为容易了。制造矛是第二步,然后又有了淬火之后的尖端和后来的石制的枪头,以增强其功能。火的可控使用也许可以回溯到80万年以前,热处理技术也至少有16万年之久了。石头制成的飞镖和箭头被证明出现在7万年前的南非地区,这只是抛掷性武器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不管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它们多么原始,这些工具使得技能要优于体型、力量和侵略性,同时鼓励了首先进攻和伏击,以及较弱个体之间的合作。认知技能的演化也是更准确的投掷、武器设计的改善和建立更可靠联盟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补充。完备的语言能力能够促进更为完备的联盟和更为强化的道德观念的建立,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回溯到最少1万年前或者最多3万年前。这些社会变化产生的具体年份大多仍然并不明确:它们可能已经依次出现在过去200万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可能更为集中地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后者就是我们这一种属的智人,他们出现在至少20万年以前的非洲大陆上。 [4]
在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累积性的结果,即地位较低的个体以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不可实行的各种方式与雄性领袖对抗的、得到改善的能力。当优势群体被置于由装备了抛掷型武器的成员所构成的群体中,且这些成员能够通过结成同盟来平衡优势群体的影响力时,公开地通过暴力和恐吓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了。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只能这样,那么暴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新的组织策略和威胁性的暴力行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矫正手段,将会发挥重要的,也可能是更为关键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类在生物和社会上的进化已经带来了一种平等性的均衡。尽管种群仍然不够大,生产能力也依然没有足够的差异化,但同样的,种群之间的冲突和地域性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多数人向少数人的屈服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动物性的统治方式和等级制度的形式已经逐渐弱化,不过它们依然还没有被建立在驯化、财产和战争基础上的新不平等形式取代。这种类型的世界大体上已经消逝了。在较低水平的资源不平等和较强的平等主义风气的界定下,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些以采集为生的人群给我们一种存在局限性的感觉,即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5]
强大的后勤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有助于在狩猎–采集者中遏制不平等。不以拥有牲畜群为特征的游牧生活方式严重限制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小规模、流动的和不稳定的觅食群体的组成方式,并不利于形成超越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基本能力的不对称关系。此外,出于刻意排除进行统治的各种尝试,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原始的平均主义。这种态度能够作为人类形成等级制度的天然倾向的一种关键性制约。人类学家已经记录了非常多的实施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方式,并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了层次划分。乞讨、行骗和盗窃有助于获得更为平等的资源分配。对独裁主义行为及其扩张的制裁方式包括谣言、批评、奚落、违抗、放逐,甚至包含谋杀在内的身体暴力。因此,领导力往往十分微妙,它分散在众多群体成员当中,且存在时间短。最开明的人对他人的影响最大。这种独特的道德经济被称为反向优势等级制:它在成年男性(他们通常支配着妇女和儿童)中发挥着作用,它也代表了权威的持续和先发制人。 [6]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这种由几百名狩猎–采集者形成的群体中,团体成员独自搜寻食物,在分配所获得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有较强的偏爱。同时,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进行食物的分享也是可以预期的行为,特别是当资源很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这种分享也是普遍的。哈扎部落可能会试图藏匿蜂蜜,因为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一旦被发现了,他们将被迫进行分享。乞讨行为是能够被容忍的,而且比较普遍。因此,即使个体明显偏向于为自己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保留更多食物,社会规范也会介入:分享是普遍的,因为缺乏统治者。较大的易腐败物品,例如大的猎物甚至可能会被分配给营地以外的成员。存储并不受重视,甚至到了可获得的资源会被立即消费掉,不会被分给那些恰好没有在场的成员的程度。结果是,哈扎部落的成员只有极少的私人财产:对女人而言是宝石、衣服、用于挖掘的棍子,以及有时是一个锅,对于男人则是弓箭、衣服和宝石,抑或是一些工具。很多商品都不是特别耐用的,所有者对它们没有形成很强的附属关系。这些基本物品之外的财产是不存在的,同时领地也没有受到保护。权威的缺乏和分散使得群体性决策很难达成,更不要说实施。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哈扎部落是现存的更广义的觅食群体的很好代表。 [7]
维持生存的觅食模式和一种平等主义的道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其他发展模式的一种可怕的阻碍,原因很简单,即需要一定程度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来激励创新和生产剩余产品,以促进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就几乎没有可供侵占和传递的剩余。道义经济妨碍了增长,增长的缺乏反过来也阻碍了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集中。消费并没有均等化,不同个体之间不仅存在身体禀赋条件上的差别,而且在支持网络和物质资源的获得上也存在差异。如我将在下一节指出的,采集者的不平等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与依靠其他生存方式的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相比,其程度是非常低的。 [8]
我们也需要容许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可能与我们农业社会之前的祖先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幸存的觅食者群体完全被边缘化了,并且被限制在农民和牧民无法达到或者基本没有兴趣的那些区域,这些区域的环境很适合上述没有物质资源积累和领地扩张需求的生活方式。在动植物被驯化来提供食物之前,觅食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更加广泛,而且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外,在一些情况中,当代的觅食者群体可能会对一个由更多等级的农民和放牧者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做出回应,并在对照外部规范的过程中自我定义。现存的觅食者同样受时间影响,并不是所谓的“活化石”,需要将他们的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9]
基于这一原因,史前人类并不需要总是像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平等化。在11700年以前(全新世开始之前时期)的墓葬中,可观察到的物质不平等虽然罕见但已经存在。最著名的因地位差异带来不平等的例子来自桑吉尔,这是位于莫斯科北面120英里 [01] 的一个更新世的遗址,其残骸存续的日期是从大约34000年前—30000年前,这一时段与上一次冰河时期中较为温和的时段相对应。它包含的是一群猎人和觅食者的遗骸,他们杀戮和消耗大型的哺乳类动物,例如野牛、马匹、驯鹿、羚羊,甚至除了狼、狐狸、灰熊和穴居狮子之外,还有猛犸。其中三个人类的墓葬显得特别突出。其中一个墓葬的特征是,一个成年男子与大约3000颗猛犸象牙制成的小珠子、大约20个吊坠和25个猛犸象牙做成的戒指埋葬在一起,这些小珠子当时可能与他的皮衣缝在了一起。另一个墓穴是一个大约10岁大的女孩和一个大约12岁大的男孩的长眠之地。这两个儿童的衣服都装饰着更多数量的象牙珠子,总数大约是10000个,他们的随葬物品还包括很多的贵重物品,例如由猛犸象牙制成的长矛和各种艺术品。
一些人一定在这些留存下来的物品上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据现代学者估计,不管在哪里,那时的人都需要花费15~45分钟来雕刻一个珠子,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人在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情况下,用1.6~4.7年来完成这些任务。最少需要抓住75只北极狐才能获取那两个儿童墓葬中的一条腰带和头饰上附着的300个牙齿装饰物,考虑到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牙齿的难度,实际需要的狐狸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尽管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会给予这一群体的成员足够多的空余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最初会希望从事这项工作。这三个人看起来没有与他们日常使用的衣服和物品埋在一起。属于儿童的那些珠子要比那个成年男子的小,这意味着这些珠子是为他们特别制作的,要么是在他们生前,要么更可能仅仅是为了他们的葬礼而制作的。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些人被视为特殊的。但显然,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成长到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的年纪,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由于家庭原因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成年男性和男童身上可能存在的致命伤,以及导致女孩一生残疾的股骨短缩,只不过增加了其中的神秘感罢了。 [10]
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还没有比桑吉尔墓葬更为壮观的墓葬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比较豪华的墓葬在更远的西方被发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摩拉维亚的下维斯拖维采,三具遗体佩戴着复杂的头饰被置放在赭石染过的地上。较晚一些的例子就更多了,利古里亚海岸的阿里纳坎迪德洞穴中建有一个很深的洞墓,墓室中那28000年或者29000年前的由红赭石染过的台子上,安放着一具配饰奢华的未成年男性遗体。他的头部周围有大量穿孔的贝壳和鹿的犬齿,它们最初可能附着在有机物制成的头饰上。除此之外,还有猛犸象牙制成的坠饰、麋鹿角做成的4个权杖,以及用外来的燧石制成的非常长的刀片也被放在了他的右手位置。大约16000年前被埋葬在圣日耳曼河旁边的年轻女性戴有贝壳和牙齿制成的装饰品,后者是大约70枚穿孔的红鹿犬齿,它们应该来自200英里以外。在大约10000年以前,仍处于采集阶段的全新世初期,一个三岁的孩子和1500颗贝珠一起埋葬在多尔多涅的拉玛德莱娜的岩棚中。 [11]
这些发现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平等出现的最早预兆。先进且标准化的手工生产、在高度重复性工作任务上的时间投资,以及使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原材料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比当代狩猎–采集者更为先进的经济活动。它也暗示了社会差异通常并不与觅食活动的存在有紧密联系:这些儿童和成年人的奢华墓葬显示出一种先天赋予的,甚至是继承的地位。尽管很难从这些材料中推断出等级关系的存在,不过这至少是一种看起来合理的选项。但是,这里没有长期的不平等的迹象。复杂性和地位差异的上升从本质上看起来还是暂时的。平等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范畴:社会行为可能因变化的环境,或者甚至是复发的周期性压力而不同。同时,获取如贝类这样的海洋食物资源的能力作为社会进化的摇篮,不仅鼓励了领土意识和高效领导能力的形成,更是最早的对沿海生活的适应。尽管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够追溯到10万年以前,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还没有新兴阶层和消费差异存在或出现的相关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旧石器时代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依然是零星和短暂的。 [12]
直到上一次冰期结束,气候条件进入一个难得的稳定期之后,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作为第一次超过了10万年的间冰期的较温暖时段,全新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善使得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能量且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也为越来越不公平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分配打下了基础。这就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侵蚀了觅食者的平等主义信念,并用一个持久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取代了这一信念。要使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就必须要有能够抵抗侵占的生产资料,并且它们的所有者要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获得剩余。通过耕种和放牧的方式进行的食物生产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采集者也能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利用那些未被驯化的自然资源。在可以捕鱼或者仅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也可能产生属地性、等级划分和不平等。这种现象,即人们所知的对海洋或者河流的适应,在人种学的档案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大约公元500年开始,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北美西海岸沿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鱼类资源的压力,促进了以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高度区域化的有鲑鱼资源的河流实施控制。这有时伴随着从人们住着大致相同的住宅的社会(无阶级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转变,这种分层社会以一所大房子里住着主人一家、随从以及奴隶为特征。 [13]
一些细致的案例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紧密联系。大约公元400—900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基特利溪旁边的遗址上,曾有一个临近费瑟河的社区,构成这个社区的几百名成员靠当地的鲑鱼维生。从这一考古遗址判断,鲑鱼的消费量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下降,哺乳动物的肉取代了其地位。在这个时候,遗迹中出现了不平等的标志。在那些最大房子的遗址坑里发现的鱼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熟的帝王鲑和红鲑鱼,两者都是富含脂肪和卡路里的珍贵奖赏食物。相对的,在两个最小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却是更为幼小和营养较少的鱼类骨头。和许多同样处于这种分层水平的社会一样,通过仪式性的再分配,不平等同时得到了赞颂和缓解:大到足够给一大批人群准备食物的烧烤坑意味着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为整个社区的人组织了宴会。1000年之后,首领之间通过展现慷慨来进行竞争的冬节仪式成为整个太平洋东北部地区的共同特征。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布里奇河遗址上,大约在公元800年,随着大型建筑的所有者开始积累贵重物品,并不再在户外准备公共食物,穷人开始依附于这些富有的家庭,不平等从此开始制度化。 [14]
在其他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和经济变得不平等。几千年来,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即现在圣芭芭拉和文图拉地区的丘马什人,一直使用着简单的船只、采集橡子,过着平均主义觅食者的生活。大约公元500—700年,丘马什人引入可供远洋航行的厚木板制成的独木舟,这种能够装载十几人并深入海洋60英里探险的独木舟使得丘马什人能够捕获更大的鱼类,并且使他们成为大洋沿岸贝壳贸易的中间人。他们把从海峡群岛获得的燧石销售给内陆部落,交换橡子、坚果和稻科植物。这就产生了一种等级制的秩序,拥有多个妻子的首领控制了独木舟,享有领土的准入权,在战争中领导他的族人,并且主持仪式性活动。作为回报,他们从追随者那里获得食物和贝壳。在这样的环境中,采集制社会的社会阶层复杂度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对于集中的本地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开始下降,同时职业的专业化、严格界定的资产所有权、边界防御,以及通常涉及奴役俘虏的相邻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15]
在觅食者当中,这种类型的适应可能仅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通常不会扩散到这个环境之外。只有食物资源得到驯化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缺失的情况下,赤裸裸的不平等可能仅仅存在于被全世界更为平等的觅食者包围的、海洋和河流沿岸的小块地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开始在不同的大陆上被驯化,首先是在距今大约11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然后是在10000年前的中国和南美、9000年前的墨西哥、7000多年前的新几内亚,以及大约5000年前的南亚、非洲和北美。而动物的驯化真正发生的时间,时而超前,时而跟随着这些创新活动。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可能是一种并不总是遵循着线性轨迹的冗长过程。 [16]
这对于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和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继任者,即这一转型的最先见证者而言,是尤为正确的。从大约14500年以前开始,更为温暖和潮湿的气候使得区域性采集者群体的规模增大,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更为稳定的定居点开展活动,他们捕获了大量的猎物且收集了数量充足的野生谷物,这让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这些食物。这种物证非常有限,但展现了一些权威专家所称的“早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征兆。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供公共使用的较为大型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花费了大力气制造出来的特殊的玄武岩研钵。根据计算,在大约14500—12800年之前的纳图夫文化早期出土的遗体中,有8%佩戴着来自几百英里外的贝壳以及一些用骨头或牙齿制成的装饰物。在其中一个遗址中,三位男性有由贝壳制成的头饰陪葬,其中一个头饰边缘有4排贝壳装饰。只有一些墓地拥有石头工具和小的雕像。大型的烧烤坑和炉床的出现可能表明,这种类型的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宴会在美洲西北部出现得更晚。 [17]
然而,无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程度在这些良性条件下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们都在距今大约12800—11700年前的、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寒冷期逐渐消失。由于当地资源的减少和资源情况的不可预测,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气候在距今大约11700年前恢复稳定,这与最早种植诸如单粒小麦、双粒小麦、小麦和大麦等野生作物的证据相吻合。在大约11500—10500年前,定居点得到了扩张,同时食物最终得以在个体家庭储存,后者表明了所有权概念的改变。一些例如黑曜石之类的外来材料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了一种表现和巩固地位的欲望。10500—8300年前这段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由不同区域组成的名为卡越努的村庄,其建筑和出土物在大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较大型的和修建得更好的建筑物装饰着罕见的和外来的工艺品,同时位于距离广场和寺庙更近的地方。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墓葬里面有黑曜石、珠子或者一些工具,卡越努村里面的4个最富有的室内墓葬中,3个坐落于紧邻广场的房子里面。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精英地位的标志。 [18]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不平等状况可能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路径。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在食物资源野生或未驯化的情况下,对水生动植物的适应能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差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引入经过驯化的马匹,将其作为运输工具,那么即便没有食物生产,也能产生不平等效应。18世纪和19世纪,在美国西南边界的科曼奇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文化,这些人依靠欧洲的马匹进行战争和长途突袭。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美洲水牛和其他野兽,他们将通过贸易及抢劫获得的玉米作为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的补充。这些安排支撑了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俘获的男孩被用来照看富人的马匹,拥有的马匹的数量将科曼奇家庭相当明确地分为“富人”、“穷人”和“非常穷”三种类型。多数情况下,觅食、种植和农业社会不总是系统地与不同水平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觅食群体可能比一些农业社群要更为不平等。一项关于北美258个印第安人社群的调查显示,物质不平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剩余的规模,而不是野生动植物驯化本身。2/3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社群都没有显现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中等或大量剩余的社群中有4/5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相关性要比不同的生存模式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强得多。 [19]
一项针对处于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发展水平的21个小规模社群,即对狩猎–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牧民和农民的合作研究,识别出了两个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土地及牲畜的所有权和将财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的能力。研究者观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财富:身体型(主要是身体力量和生殖能力)、关系型(例如劳动中的伙伴关系)和物质型(家庭物品、土地和牲畜)。在这些样本中,身体型的禀赋是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当中最为重要的财富类型,物质财富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对牧民和农民而言则是相反的。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权重是调节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身体型的禀赋对身体约束是相对严格的,特别是对身材大小而言,对力量、狩猎能力和繁殖成效而言则稍微少一些。关系型禀赋,尽管更为灵活,但在农民和牧民当中分布得更不均衡,这两个群体中,以土地和牲畜为代表的不平等程度测度,要比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之间以器皿和船只为代表的测度水平更高。不同类型财富的各种不平等约束和特定类型财富的相对重要性的结合,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生存模式的一些差异。平均的复合财富基尼系数对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而言低到了0.25~0.27,但是对牧民和农民而言要高得多,分别是0.42和0.48。仅就物质财富而言,主要的差别似乎在觅食者(0.36)和所有其他人群之间(0.51~0.57)。 [20]
财富的可传递性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代际财富传递的程度对农民和牧民而言,要比其他人高出两倍,同时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要比狩猎–采集者和种植者的资产更适合传递。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顶端,他们的孩子最终也将位于相同的位置,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些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底端的孩子在未来所处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些系统性的差异对于人生际遇的不平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这种方式定义,跨代的流动性通常是平缓的:即使在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中间,处在前1/10家庭的后代复制这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处于最后1/10想要向上爬升的这些家庭的高出至少3倍。然而,对农民而言,这一概率更大(约11倍)。对于牧民就更加高了(约20倍)。这些差异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技术决定了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重要性和特征;另一个因素为控制财富转移模式的制度,例如农耕和游牧民族倾向于向亲属垂直转移。 [21]
根据这一分析,不平等及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是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别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可传递性以及实际传递的比例。因此,那些物质财富作用不大、财产不便于传递以及继承受限的群体,注定要比那些物质财富是主要的财富类别且有高度可传递性,同时被允许留给下一代的群体所感受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要低。长期来看,可传递性是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财富在两代之间进行传递,那么产生不平等的因素,诸如与健康有关的随机冲击、平等性、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将会得到保持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不会使分配性的结果回归到均值水平。 [22]
与前文提到的对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结果一致,从这21个小规模的社群样本得到的实证发现同样表明,动植物的驯化并不是显著不平等化的充分条件。对可保护的自然资源的依赖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些通常能够遗赠给下一代。在类似翻耕、修建梯田和灌溉上的投资同样也是如此。这种生产性资产及它们的改进的可继承性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不平等:一方面,两者都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减少了代际间的差异和流动性。一项对超过1000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更广泛的调查,证实了传递的核心作用。根据这个全球数据库,大约1/3的采集者社会对于动产有继承的规则,但是只有1/12的社会认可不动产的继承。相形之下,几乎所有开展了集约形式农业的社会都具备涵盖这两种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则。复杂的觅食者和种植者社会则取乎其中。继承是以财产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我们只能推测它们产生的环境条件:塞缪尔·鲍尔斯认为,耕种有利于形成那些对采集者而言没有用或者不可行的财产权利,因为像谷物、建筑和牲畜这样的资源很容易就能被限定清楚并保护,这些前提条件是采集者所依赖的那些分散的自然资源不具备的。水生物的适应以及驯马文化这些例外情况也完全符合这一解释。 [23]
历史上,不平等现象有时会出现得很缓慢。恰塔霍裕克是安那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几千个居民兼顾种植和放牧。土地很充裕,它没有类似政府的结构或者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居民居住在他们储藏粮食、水果和坚果的家庭住房里面。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工艺品。在对从公元前7400—前6000年的20座建筑和9个庭院的2429件物品的全面考察中,人们发现了特定类型的器物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完整的磨盘和手推石磨在各个家庭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过这些家庭一般都有多种烹煮器具和石制的工具。完好的手推磨主要发现于装饰更好的建筑中,但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这到底是代表了这些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还是它们仅仅承担了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合作工序。大多数磨盘和手推磨都存在在它们完全损耗之前很久就被故意毁坏的现象,可能对前面的第一个推测形成反驳。这一习惯甚至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对有价值资产的代际传递的禁止,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禁令,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后期,手推磨在可传承的财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矫正措施的积极实施限制了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24]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逐渐成为常态。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一区域第一批国家建立的很久以前,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的标志。例如,在现代巴格达北面的底格里斯河岸边,埃斯–索万遗址中的村落,有一座带有壕沟的土墙,以及很多投石器使用的、由黏土制成的投掷物,这些表明了大约7000年前的暴力冲突,以及有助于中央集权领导和等级制度创立的条件。在这一遗址上,一些豪华的墓葬是为儿童准备的,这就反映了一种基于家庭财富而不是个人成就的地位差异。大体上与前者处于同一时期的,靠近摩苏尔的阿尔帕契亚遗址,更像是一个精英阶层家庭的住所,里面有着大量的房间,以及精美的陶器、雪花石膏制成的容器,各种类型的黑曜石装饰品和手工工具。在这个定居点,首领通过给未干燥的黏土团刻上简单的印记来加封货物的方式控制贸易——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复杂封印的早期先驱。据说在耶里姆山丘,一具火化的年轻人遗体不仅和一些黑曜石珠子埋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封印工具,这标志着他可能是一位官员的后代或者是其指定的继承人。 [25]
在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各种防御性结构和对有效领导力的需求,可能与多种政府功能有关的世俗性公共建筑,强调仪式性权力重要性的神殿和庙宇,以奢华的儿童墓葬为典型例证的世袭地位标志,以及不同定居点中精英阶层家庭之间工艺品交换的证据。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发展分化了人口,尊贵的地位、对经济交易的控制以及个人财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其他环境中,政治领导地位开始与高水平的物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今保加利亚黑海岸边的瓦尔纳的一个墓地,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有超过200个被占据的墓穴。其中一个墓葬比较突出,一个中年男子与不少于990个、总重超过了3磅 [02] 的黄金物品安放在一起:他身上覆盖着可能是附着在他原来所穿的衣服上的黄金饰品,胳膊上戴着很重的金环,手中持一个斧型的权杖,甚至他的下体也套上了黄金。该男子墓葬中出土的黄金物品的数量占该遗址总出土黄金物品数量的1/3,重量占了1/4。随葬品的总体分布非常不均衡:超过一半的墓葬里有随葬品,但只有不到1/10的墓葬中随葬品种类丰富,只有少数几个墓葬拥有包括黄金在内的大量随葬品。根据时期的不同,每个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的基尼系数为0.61~0.77,但是如果我们用价值来调整这一分布,该数值就会更高。尽管我们只能对这一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猜测,但其等级结构的特征几乎不用置疑。这个被黄金覆盖的男子和他的很少的同类极有可能都是地位崇高的首领。 [26]
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不平等的补充来源:来自可保护资源的剩余和个人或家庭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将它们转移给后代或其他亲属的权利)。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上的分层奠定了基础。各种新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促进并且放大了由此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如同向食物驯化转变一样,政治等级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并且高度取决于生态环境、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在长期,总体的变化方向是从只有几十人、小规模家庭组织、以简单觅食者经济为特征的本地群体,向通常具有数百位成员的本地群体和集体,向控制几千或者几万人的更大的酋邦或原始国家的转变。这并不总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同时,不是所有的环境条件都能支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果,基于农业的复杂的国家级别的社会最终与联盟、部落、游牧酋邦、种植者,以及从古代一些狩猎–采集者群体遗存下来的人一起在这个地球上共存了。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理解促使不平等出现的背后的力量至关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生存模式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们对于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财富的积累、传递和集中的重要性。 [27]
在世界范围内,有记载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形式的范围同样较大,这使得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关联起来成为可能。在全球视角下,农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超过1000个社群的样本中,超过3/4的简单采集制的社群没有表现出社会分层的迹象,与之相对的是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社群只有不到1/3的人有此现象。政治等级制度甚至更为强烈地依赖于定居式的农业:实际上,精英阶层和阶级结构在简单的采集社会中是看不到的,但这二者被证实存在于大多数农业社会中。然而同样的,是经济剩余的规模而不是这样的生存模式本身起到了关键性变量的作用。在前文提到的针对258个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调查当中,86%的没有明显剩余产生的群体缺乏政治不平等的迹象,那些产生了中等或者大规模剩余的群体中,有同样比例的群体已经发展出至少某种程度的政治等级制度。在186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着更为详细记录的社会,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跨文化样本当中,4/5的狩猎–采集者社群没有首领,3/4的农业社会组成了酋邦或者国家。 [28]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一项新的全球调查显示,谷物的培育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那些能够持续供给但是会很快腐烂的多年生植物不同,粮食作物只能在特定的收获时节一起收割,并且适合长期储存。这两个特点都使其更容易被精英阶层占有,且精英阶层控制剩余的食物资源。国家最早出现在那些首先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一旦植物,特别是谷物和动物开始被驯化,人类早晚也会被等级制度驯化,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到此前难以想象的高度。 [29]
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然而,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起来,不仅会加重既存的不平等状态,还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前现代国家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措施,并且为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开辟新的私利获取渠道,从而为资源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物质的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量的每一个增量都很可能引起其他变量产生相应增量。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定义,试图捕捉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借用他们的几个要素,国家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政治组织,它声称自己拥有领土及其人口和资源,它拥有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颁发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来履行政府职能,并通过威胁和实施包括暴力在内的合法的强制性措施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对于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并不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公认的驱动力量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口的影响: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通过控制贸易流获得的收益,对授权领导人管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更加复杂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需求,源自生产资料获取方式的阶级冲突,以及能够强化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稀缺资源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压力。 [30]
从不平等研究的视角来看,严格地说,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的形成给社会带来陡峭且稳定的等级制度以及大量剩余与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物质财富却是必然增长的。即便如此,现在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共识认为,组织化的暴力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罗伯特·卡内罗影响广泛的限制理论认为,在领土有限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和战争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更为自治和平等的家庭,在依赖稀缺的已驯化的食物资源且无法摆脱有压力的外部环境时,人们臣服于独裁的领导者且忍受不平等以便更有效地与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最近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仿真模型同样强调了群体之间冲突的极端重要性。暴力的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大多数前现代国家的具体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专制的统治,以及对发动战争的强烈关注。 [31]
并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与更多的“异质”或者企业形式的政治组织共同存在。即使是这样,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一般要比不同结构的对手更胜一筹。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它们就会在全世界独立出现,无论是在旧世界、美洲大陆,还是跨越了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冲积平原到安第斯的高原的一系列不同环境,均是如此。无视巨大的背景差异,它们中最著名的国家都发展为异常相似的实体。它们中都出现了在不同领域中的等级制度的扩张,从政治领域到家庭和宗教信仰系统——这是一个自我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制度结构会对所有社会因素做出反应,使它们更好地融入支撑权力结构的整体系统”。阶层分化的加剧,对道德价值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对不平等的优点的信仰和接受等级制度是自然和宇宙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取代了古代平等主义思想的残余。 [32]
在数量的意义上,农业国家表现得极为成功。尽管这些数字更多只是一种比较克制的推测,我们依然可以猜想,3500年以前,当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也许仅仅覆盖不超过1%的地球陆地表面的时候(不包括南极洲),它们已经控制了大约一半数量的人类。在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估计,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庞大的帝国,如罗马和中国的汉朝占据了大约1/10的地球土地面积,但拥有那时所有人口的2/3~3/4。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这些数字传达了特定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庞大的帝国结构由强有力的榨取型精英阶层连接在一起。同样的,这不是唯一的结果:独立的城邦也可能在这些帝国之间的缝隙中繁荣发展,但是很少能够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那样成功地抵抗住它们庞大的邻国。它们往往被吸收进更大的实体;偶尔,它们也会建立自己的帝国,例如罗马、威尼斯和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此外,这些帝国也会衰落,让位给更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中世纪的欧洲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33]
然而,更为常见的是,随着新的征服者政权重新巩固较早的权力网络,帝国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帝国。从长远来看,这就造成了一种从不断变得更有规律的中国的“王朝周期”到东南亚、印度、中东和黎凡特、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脉区域的较长期波动的周期性颠覆与复原的模式。欧亚草原地区在位于其南方的农耕社会产生的财富的刺激下,也催生了很多从事掠夺性袭击和征服的帝国政权。国家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地球上最大的帝国的面积是几十万平方英里 [03] 。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其最强有力的继承者在常规上都会以一整个数量级的程度超过这一数值,到13世纪,蒙古帝国范围从中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时,领土只是其中一种度量标准:如果我们用人口密度来解释长期性增长,我们会看到帝国统治的有效扩张甚至是更为剧烈的。在比今天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我们人类曾经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温带、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这些就是帝国繁荣发展的地区:几千年来,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这些庞然大物的阴影中,其中一些走到了远高于平民百姓的地位之上。这就是创造了我所定义的“最初的1%”的历史环境,是由竞争性但经常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精英群体所构成的,这些群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捕捉由国家建立和帝国整合所调动起来的政治租金和商业收益。 [34]
前现代国家的形成将少数统治阶级从大量的初级生产者中分离出来。尽管常常在内部还有分层,精英阶层超越并集体控制了形成国家基本建设单位的独立本地社区。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名图形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反映了这些结构(见图1.1)。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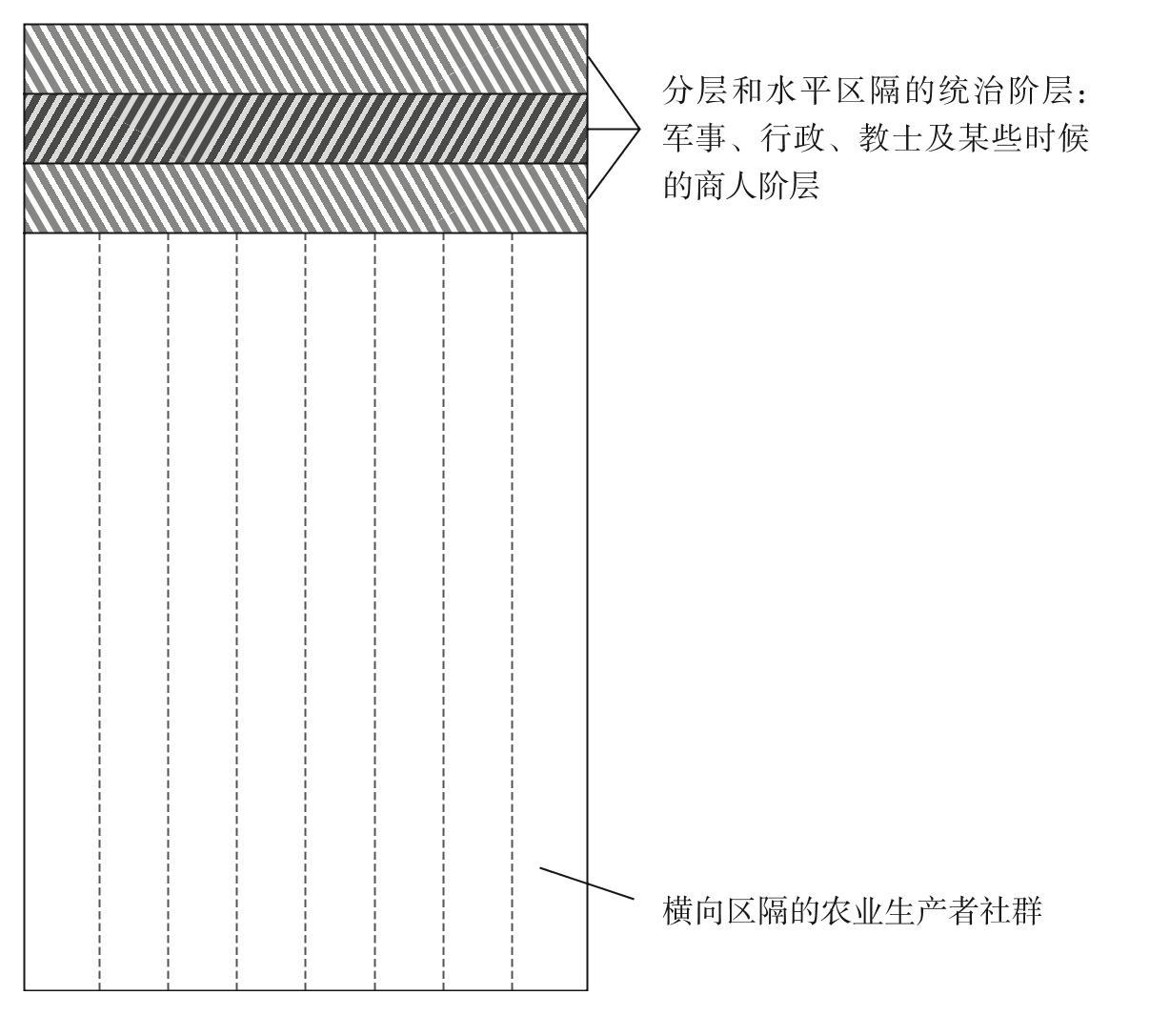
图1.1 农业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
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例如登上国家公务员位置或者获得相关荣誉的本地名流,本就起源于或者甚至会一直扎根于这些社区,而其他人,例如外国征服者,可能会与之足够分离以在实质上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以现代标准来看,中央集权统治是很有限的:国家通常只是略微强于帕特里夏·克龙所称的一般民众的“保护性外壳”,试图排除对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国内外挑战。但是,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也以类似现代社会的的黑手党组织所用的方式提供保护,利用他们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利润。因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太弱,无法限制精英阶层的行为,后者常常使用大量的专制权力,包括行使对生杀以及财产分配的权力。同时,许多国家都缺乏一些基础性的权力,即社会渗透和广泛实施政策的能力。这些社会大体上都是自治的,由一个相对较小而且常常遥远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进行松散的控制。
政府在本质上是半私有的,同时依赖选举,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同掌控者的合作来控制从属群体,为统治者调动资源。后者倾向于使用奖励和暴力威胁混合的方式来保持竞争性的精英阶层之间的平衡,因为政府常常专注于管理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群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大地主这些通常相互交叉的群体,陷入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当中,这些剩余可能通过政府税收和私人租金而被抽走。然而,雇用资深的精英阶层成员作为政府官员限制了统治者的自主能力,求助于地位较低的下级代理人则会创造出新的精英群体,他们热衷于为了加入现有的精英群体圈子而转移政府收入,将来自职位的收益私有化。统治者竭力获得权力,同时给予政府服务一种附带和可撤销的特权,然而他们的代理人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私人利益。长期下来,后者常常被证明是更成功的。腐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掠夺都是普遍的。当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了地位和好处竞争的时候,个体之间的流动比例可能是比较高的,然而这样的精英统治只要政权结构成功得以保持就会倾向于维持稳定。上层社会群体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而与普通民众分隔开,这种世界观常常在本质上是尚武的,而且将统治者定义为劣等的农业生产者的剥削者。炫耀性消费成为彰显和强化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 [36]
这些基本条件深刻地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精简之后,历史上仅存在两种理想类型的财富获取方式:制造和索取。生产剩余的出现、动植物驯化和可继承的财产权为个人财富的创造和保持开辟了道路。长期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进行,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及范围提高了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上限,因此至少增加了收入和生产性资产分布的可能范围。原则上,随机冲击的累积效应已经足够使得一些家庭比另一些更为富裕:土地、牲畜、建筑,以及在贷款和贸易商投入资源上的回报差异会使得这一切变得确定。在他们的财富变化之后,其他人会取代他们的位置。
能够说明次一级精英圈子中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的最早的可量化证据,可能来自几千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古巴比伦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的上半叶)男性子孙继承比例的样本与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有记载的女孩嫁妆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明显的差别。转换成以小麦计算的工资之后,后者大约是前者数量的两倍。这两个数据好像都指向的是同一阶层——城市居民,他们可能在城市人口中处于收入分层的顶部。这就表明了更大的整体性的富裕,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本来期望儿子要比女儿更受偏爱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这些嫁妆的实际价值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新巴比伦时期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动态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对比也许由增长和商业化的不平等效应来解释最好。 [37]
然而,不管是在这个案例中还是更为普遍的,这可能仅仅是事情的某一方面。鉴别我们已经描绘出来的前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明显特征,及其会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是比较容易的。政治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扩大市场和至少降低一些交易和信息成本:作为前现代政治一般特征的普遍性权力不对称,几乎一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的是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脆弱的产权保护、不适当的规则执行、随意伸张正义、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极端重要的人际关系与强制性权力,以上都是一些可能扭曲有利于在地位金字塔上层的人和那些与他们有利联系起来的人的因素。这对统治阶级成员和他们的伙伴可获得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各种形式的“获取”来说也是成立的。参与治理从正式的补偿、统治者和其他上级的恩惠、索取贿赂、侵吞公款和勒索钱财等方面开拓了获得收入的渠道,而且它也常常提供税收和其他义务的庇护所。高级军事职务可能会使某人获得战利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为国家直接提供服务甚至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亲属关系、通婚,以及其他与高官的联盟也会产生相当的利益。此外,考虑到通常相当有限的政府基础能力,个人财富和本地影响力使得保护个人财产以及朋友和委托人的财产(用以交换其他利益)免受国家或者社区的索取更为容易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将额外负担转移到弱势群体以满足税收配额的要求。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权力可能几乎无法对物质财富的分配施加重要的影响。在更小和较少等级划分的政治组织中,例如部落或者上层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与整个社会分享其成果的意愿。农业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通常享受更大的自主权。尽管偶尔会有大量公开的赏赐,但再分配的流向往往趋于逆转,即以多数人为代价使得少数人更富有了。精英阶层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的集体能力决定了能被占用的总资源的比例,国家统治者和各种精英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了这些收益是如何在国库、政府官员的私人账户、地主的不动产和拥有商业财富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 [38]
将资源导向掌权者的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也可以作为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有力制约。不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掠夺行为和权威的任意使用有助于创造出财富,同样,在一瞬间摧毁财富也很容易。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接近权力和统治者使得那些有关系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竞争对手耍阴谋,同时统治者意图限制其伙伴,侵吞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收益,这些举动都可能夺去他们的性命,至少可以很轻易地抢走他们的财富。除了家庭人口的异常变化有助于解释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传递以外,暴力性的再分配限制了资源集中到精英圈子中的程度。
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中世纪埃及的马穆鲁克占据了这一分布光谱的其中一极。外来的和非世袭征服者精英阶层集体性地拥有了对土地的控制权,视统治阶级成员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土地分配,这一位置也会时常被调整。这就使得资源的获取更为易变和不可预测,因为暴力性的派系争端带来了较高的转换率。在这一分布光谱的另一极,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或欧洲中世纪时的封建社会,弱势的统治者使得贵族能更有把握地保住他们自己的资产。这对处于灭亡危机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来说也是如此,当贵族一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统治政权的时候,都恰当地热衷于支持私有产权。大多数的前现代社会及相当多的当代发展中国家,都位于这两个理想类型的中间,将偶尔对于私人产权关系的暴力性政治干涉与对个人财富一定程度的尊重结合起来了。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关系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39]
从政治权力的获取中取得租金并不只局限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对西方国家很多超级企业家富豪的一项最新研究,展现了这些富豪是如何从政治关联、利用监管的法律漏洞和利用市场不完全性中获利的。在这一方面,发达的民主制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在一些例子当中,估测出精英的财富有多少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收入来源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太过富有,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农业和商业就逐步变得这么富有,那么对于更为晚近的社会,更为具体的统计分析应该也是可行的。我随后分析的旧君主制度下的法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在最一般化的意义上,几乎不用怀疑,之前个人化的政治关联和偏爱要比它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对精英阶层的财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拉丁美洲和非洲精英阶层的寻租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近在全球史意义上传统的和确实“正常”的财富占有和集中策略。俄国的“寡头”也是如此,他们与一些前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他们财富的创造和维持都依赖于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关系。即使考虑到具有很大不同的背景,俄罗斯的信用卡大亨奥列格·京科夫对其同类人的描述——“资产的暂时管理人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在同等程度上适用于从古罗马到中国,一直到近代欧洲早期的君主的不稳定地位。 [40]
皮凯蒂寻求用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回报之间的较大差距(“r >g ”),来解释非常高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成为18和19世纪欧洲典型特征的原因。在以可乘可加冲击为特征的动态模型中,对资本回报率的冲击与投资策略或运气相关,人口参数产生于死亡率和奇偶校验,有关消费和储蓄的偏好,加入外部收入的生产率的冲击,这些条件更倾向于放大初始财富差异并带来更高程度的财富集中。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时以战时破坏、通货膨胀、税收和征用等形式对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所产生的负面冲击极大地减少了财富,从财富获得的净收入更是如此,这一大矫正时期之前的更稳定的条件对于财富的持有者比较有利。结果,来自资本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更大比重。
这种情况是前现代社会更具普遍性的代表吗?鉴于经济增长率和名义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由利息率或者由来自不动产或禀赋的固定收益表示)总是非常大,假设在总体上资本所有者享有一种长期的优势似乎是合理的。同时,我们预计,资本受到冲击的程度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取决于资产剧烈再分配的可能性。在稳定的时代,独裁统治的恣意妄为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的财富更是如此,这些财富可能常常发生膨胀),就如同它能摧毁那些财富一样。只要这种干预仅仅是再分配已经被社会的顶层声称占有的资产,对财富分配的总体效应很可能是中性的。相对的,由战争、征服或者国家灭亡产生的冲击带来的是不太可预测的结果:尽管军事成功可能通过使其统治阶级更为富有提升了胜利一方的不平等程度,但整体上矫正效应通常会从政权结构的崩溃中产生。我在本章和后续几章为这些发展过程提供了历史证据。
长期来说,财富不平等的水平一定是由这些更不稳定的暴力性冲突发生的频率塑造的。到目前为止,早期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机制与我们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存在差异,它们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精英阶层从劳动力以外的资源获得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个人财富越是依赖于政治租金的获取,更多来自劳动力的收入(如果我们至少可以明确腐败、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军事掠夺、争夺恩惠,以及夺取对手劳动力形式的资产)比起更为有序与和平的社会中的企业家或食利的资本投资者所起到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同我在之后这一部分中所谈到的,这种本质上的收入可能是主要的,有时甚或是精英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早期的古代国家特别正确,它们的上层阶级更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租金收益,而不是私人资产回报。这些授权符合传统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同时再一次强调了政治权力关系在创造“最初的1%”当中的极端重要性。 [41]
*
相当平均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曾经在很多后来开始建立大帝国的区域普遍存在。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即一个从文字资料得知的、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的最早期文明中,大量的农地曾经是由那些把它作为公有土地进行耕作的,延伸的父系平民家庭控制的。这种类型的所有制在中国商周时期也比较普遍,在那时,私有土地买卖是不被允许的。在阿兹特克时期的墨西哥谷地,大多数土地是由“卡波廷”所拥有和耕种的,这是一种社团组织,它拥有的土地包括家庭领地和公地。前者有时候会周期性地进行重新组合以考虑家庭规模的变化。印加帝国时期秘鲁高原中的“阿鲁昆纳”同样也是如此,同族婚配的群体将不同海拔的地块分配给单个的成员家庭,同时定期地对其进行调整以保证分配公平。这一类的安排对于土地的集中和商业开发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资本拥有者获得土地,以及政治领导人对现有的资产强加进贡规定之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当苏美尔人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3000年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大量土地并且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的寺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已经积累了相当大量的资产。只要其他群组成员同意这样,世袭领地的私有化也是可能的。债务可以作为将剩余收入转化为更多土地的有力工具:高达1/3的年利率迫使那些借款人把他们的资产让渡给贷款人,如果他们承诺以自己为担保,那么甚至可能被迫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大的不动产,也带来了耕种它们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债权人也许可以从管理他们自己的经济资产中得到一些用来借给他人的可支配资源,同时政治租金能在为他们提供追求这一策略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私有化减少了委托人和支持者的传统社会义务:附着于私有财产上的社会责任越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那时已经发展出多种社会地位以迎合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佃农和债务奴隶,奴隶这种更为原始的从属类型也被添加到这一组合当中。我们能在4000年后观察到类似的过程,但是在一个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农村债务、无地农奴和奴隶支撑了不断上升的不平等趋势。 [42]
国家统治者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侵占的模型,常常也是侵占的手段。苏美尔国王试图让自己和追随者获得土地,慢慢地潜入寺庙不动产的经营过程中,以获得对资产的控制。庙宇的管理人员把机构资产的管理与他们自己资产的管理混在了一起。渎职、贪污和武力都是早已形成的将资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公元前24世纪拉格什城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记录表明,当地的国王和王后接管了寺庙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工人;贵族通过取消高利贷的赎回权获得土地;官员滥用船只和渔场这类的政府资产,对例如葬礼和剪羊毛这样的基本服务收取高价,扣发工人的工资,同时普遍地通过腐败来充实自己的口袋;富人从穷人的鱼塘偷鱼。先不谈这类指责有一些好处,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种特别的鼓励侵占和为个人利益而使用权利来致富的统治方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断在精英圈子中进行的收购和私有财产的集中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他们需要保护初级生产者免受掠夺性放贷人和支配性的地主的压迫,因为这些生产者被寄予了支付税收和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的期望。从公元前31世纪中叶—前21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定期地发布取消债务的命令,试图减缓私有资本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会失败的战争。 [43]
我们能在“赦免之歌”中找到关于这些紧张关系的生动例子。这是一个在公元前15世纪被翻译成赫梯语的胡里安神话。它描写了胡里安人的天气之神泰舒卜,他伪装成一个债务人出现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埃卜拉市政厅中,形容枯槁且看起来亟待帮助。梅吉国王与该城中的强权贵族在释放债务奴隶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是一项被认为需要神的命令的措施,但成功地被扎扎拉这位能左右精英阶层会议意见的天才演说家反驳了。在他的影响下,议员愿意在泰舒卜欠债的时候提供金银作为礼物,在他干涸的时候提供油,在他冷的时候提供柴火,但就是拒绝按照梅吉的希望释放债务奴隶:
但是我们将不会释放(奴隶)。梅吉,你的灵魂深处将不会有喜悦。
他们提出了保持对借债人的这种束缚的必要原因:
假如我们释放他们,那么谁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呢?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斟酒人,另一方面,他们为我们准备食物。他们是我们的厨师,并且为我们清洗餐具。
梅吉面对他们的难以管束只能哭诉,并且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对奴隶的权力。恰好在这一留存下来的文本中断之前,文中写道,泰舒卜承诺如果其他债务得到免除,将会给予他们神圣的奖励,并且威胁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44]
这样的一些描述反映了面对精英的特权和侵占行为时,皇室权力的局限性。古代西亚城市中的国王,也不得不在与本地庙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竞争中小心翼翼地增加他们自己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很多这种政治组织的平衡和相对适中的规模成为不平等干预的一种制约。然而,大规模的征服显著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对竞争对手和其领土的暴力性占领,为更为公开的掠夺以及不受传统本地约束条件限制的财富积累打开了大门。现有国家组织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并创造出新的等级层次,从更宽广资源的基础上给身居高位的那些人获得剩余的路径。几乎不能通过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来强化总体不平等的经济发展。
通过大范围的征服形成国家的不平等效应,在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的阿卡德王国的例子中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规模上,也从多种族的异质性、非对称的中心–外围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荣誉和等级的传统意义上定义帝国,这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对从叙利亚北部到伊朗西部的多元化社会行使着权力。这种前无古人的扩张不仅鼓动阿卡德的统治者要获得神圣的地位(现存的文本指出,里木什作为帝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的儿子和继承人,“认为自己属于众神的一员”,他的侄子纳拉姆辛宣称“他的城市的人要求他成为他们的阿加德城之神,并且他们在此为他修建了庙宇”),而且大规模地获取和再分配资产。当地城邦的国王被阿卡德任命的总督取代了,同时大量的土地最终都到了新的统治者和他们资深的代理人手中。由于大量最有生产力的农田都由寺庙掌握,统治者或者没收这些土地,或者指派他们的亲属和官员作为教士以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新的帝国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地产。他们将被征用的土地分给了过去支持他们的官员,并用其奖励他们自己的随从和下属,其中一些被称为“天选之人”。后来的传统表现出对“在草原上分配农田的抄写员”的反感。政府拨款的受益人通过购买私人土地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产。
一些阿卡德人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神王纳拉姆辛的管家耶蒂–梅尔在帝国的不同区域拥有差不多2500英亩 [04] 的土地。梅萨,公元前23世纪末的一位显要人物,控制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他被授予了其中的1/3,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购买了剩下的土地的使用权。他的土地被分给了更低级的管理者、手艺人和随从,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超过90英亩的较大份额,大多数人不得不获得非常小的地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剧增加。再加上掌权者很少顾及既有的所有权模式的重新分配资产的能力,生产性资源在帝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环境,为一小部分的精英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一位著名的专家断言,“阿卡德的统治精英享受的资源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苏美尔贵族所认知的水平”。 [45]
帝国的架构有潜力以一种与经济活动的回报不相关的方式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将物质不平等变为权力关系重组的副产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使企业家投资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善商业活动的整体环境。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都市的中心,从而也加剧了物质不平等。它使大众需求和期望免受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富有的精英阶层的影响,给予他们追求个人收益上的更完全的自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但是,帝国的统治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塑造了不平等。国家主导的对政治精英成员和行政人员的物质资源分配,将政治不平等转变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直接且迅速地在经济领域再造了权力不对等。前现代国家中权力代表制的本质要求统治者与他们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原有的精英一起分享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生产性资产而言,指定剩余的拥有权可能比正式的产权更为重要。这在那些劳动力提供的服务代表着国家和精英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别正确。在印加帝国,劳役安排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的记录,但强制性劳役在埃及、西亚、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也很普遍。授予土地几乎是一个赏赐核心伙伴的普遍方式,夏威夷的酋长、阿卡德和库斯科的神王、埃及的法老和周朝的天子、中世纪的国王和新世界的查尔斯五世都分配过土地。他们试图让这些受俸的不动产在初始受益人的家族中被继承,并且最终它们变成私有财产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即使当其成功实现的时候,这些转变仅仅是延续和固化了起源于政治领域的物质不平等。
在土地和劳动力的授予之外,参与国家财政的征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精英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这一过程得到了如此好的证明,以至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对其进行分析。这里只给出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例子,在奥约帝国,即现代社会早期、西非的一个较大的约鲁巴国家,各地的小王和臣属的酋长在参加首都举行的年度盛会之前都聚集在当地的朝贡中心。作为贡品的贝壳、牲畜、肉类、面粉和建筑材料,通过一些官员被献给国王,这些官员被指定担当特定进贡者群体的代表,并且有资格获得这些贡品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承担麻烦任务的补偿。不用说,正式的报酬常常只是这些财政官员从他们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适中比例。 [46]
到3000多年前的中巴比伦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帝国王朝教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一个重要的道理——“国王就是财富走向其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了解了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一点其实几千年来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暴力性掠夺和政治偏好极大地补充和扩大了源于生产剩余和继承性资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初的1%”。我无法使得布鲁斯·特里杰对于阿兹特克贵族的精辟描述更进一步,他写道:
(他们)穿着棉质衣服、凉鞋,戴着羽毛制品和玉石装饰品,居住在双层的石屋中,吃着人们进贡的鲜肉,公开喝着巧克力和发酵饮品(适度地),娶小妾,随意进入皇宫,能在宫廷餐厅进餐,在公共仪式上表演特殊的舞蹈。而且,他们不用纳税。 [47]
一言以蔽之,这是前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公开面目。出于他们同类相残的癖好,这一特定的精英阶层得以将那种对他们来说甚为常见的,靠榨取他人血汗来维系的消费,提升到一个难以言表的程度。对人类历史的多数情况而言,非常富有的人确实“不同于你我”——甚或是我们更为普通的祖先。物质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身体。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医疗知识的进步最终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之时,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群众所周知地俯瞰着发育迟缓的群众。如果这些看起来不太(很不)完美的数据是可以信赖的,这种差异可以在时间上拉回到更久之前。埃及的法老和青铜器时代希腊的迈锡尼的精英似乎显得比普通民众高一些。一些严重等级分化社会中的骨骼数据表明,其身高上的差别要比那些分层化不太强烈的社会的大一些。最后,最重要的是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随着精英拥有更多女眷并繁育了大量后代,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48]
诚然,前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由其人脉深远的精英群体的贪婪所单独决定的。来自古代巴比伦的次精英圈子中遗产和嫁妆差异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影响下的不断上升的差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下一章和第9章中,我提供了在欧洲和北非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统治之前、中间和之后不同时期有关房子规模的考古证据,这些反映了城市平民在消费不平等上的明显差异。即便如此,尽管毫无疑问可以举出更多材料(特别是在葬礼的记录中,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收集关于普通人群中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有意义的信息。 [49]
但是,我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用主义而聚焦富有的人群。就像我们将会在第3章和附录中看到的,在很多例子当中,社会调查或者人口普查记录使得我们至少能在非常粗略的线索上追踪,从古代到现代殖民时期特定社会当中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这些大概的估计能够画出来的洛伦茨曲线,大多都像曲棍球杆,而不是月牙形的,这表明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古希腊和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这些我会在第3章和第6章讨论的群体),在国家水平的政权中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一般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资源可能可以与精英群体的财富相抗衡。仅仅是这一原因,不平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源比例调节的。 [50]
最后,引入大量非常贫困的个体也会提高整体的不平等水平。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奴役和放逐外来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新亚述帝国在从事大规模的强迫性重新安置方面臭名昭著,其中大多数是从被征服的边缘地区安置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核心区域的。大规模的转移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帝国的扩张和统一正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关于这一古代记录的一项调查得到了涉及1210928名被放逐者的43个事件,以及超过100个的我们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部分数据的放逐事件。即使这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尽管关于把所有人群赶出家园的论断需要小心对待——“他的土地上的人们,男的女的,小的大的,都没有例外,我带领他们前进,我把他们视作战利品”——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
大约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被放逐者的不断流入使得亚述国王得以建造、转移和供养几个都城。歌颂皇室功勋的石头浮雕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被放逐者仅能携带少得不能再少的个人物品,例如一个包或者麻袋。他们被剥夺了以前的资产,一般只能期望勉强维持生存。当帝国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们的状况甚至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相关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重新定居的对象被正式地与土著居民区别开来:他们“与亚述人在一起”。从大约公元前705—前627年,大胜仗和不断持续的扩张培育出一种高涨的优越感,这种语句在亚述征服者的最后阶段消失了。被放逐者被降级到劳力的地位且被用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中。
强制性移民不仅扩大了穷人的队伍,而且提高了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法庭和寺庙的多种文本都提到了战俘的分配。当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国王从埃兰(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拖来大量的被放逐者的时候,他宣称这些是“我奉献给我的神灵的精品……这些士兵……我增加了我的皇家军队……剩下的在都城中、在伟大的神的驻所、在我的官员、在我的贵族和我整个阵营中间像绵羊一样进行分割”。分配后的这些俘虏被放到授予官员的农田和果园中进行劳作,其他人被安排到皇家土地上。由于是在很大规模上实施的,这些安排提高了劳动者在整个有着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了那些接近上层的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注定会恶化整体不平等的组合。 [51]
奴隶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对外来人口的奴役是少数几种能够在小规模的,有着较低或适中复杂性的采集者社会创造出显著不平等水平的机制之一,这不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维生的觅食者社会中,还广泛地存在于部落群体中。然而又一次的,驯化和国家的形成促使对奴隶的使用达到新的高度。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几百万奴隶进入意大利半岛,他们中很多人被富有阶层买来,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农庄中辛苦工作。2000年之后的19世纪,在现在的尼日利亚,与“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提高了其物质不平等恰好同时发生的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也将大量的战俘分配给其政治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成员。 [52]
[1] Boehm 1999: 16–42是一个经典文献。特别是参见其130~137页关于所有这些物种中的社会关系被定义为(或多或少的)“暴虐”的原因。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当中,大规模死亡形式的暴力性冲击也可能缓和等级差异,同时减少基于地位的欺凌:Sapolsky and Share 2004。
[2] 关于这些物种形成的时间,参见Pozzi et al.2014: 177 fig.2,这是写作本书时可以得到的最新和最全面的研究。将来的研究完全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仅仅三年以前,Tinh et al.2011: 4就已经提出了明显更晚的时间点。Traits of common ancestor: Boehm 1999: 154.
[3] Orthodoxy: Klein 2009: 197.Plavcan 2012: 49–50 rejects the notion of lower dimorphism,comparable to modern human levels, already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proposed by Reno, McCollum, Meindl, and Lovejoy 2010; Reno and Lovejoy 2015.Cf.also Shultziner et al.2010: 330–331.See Plavcan 2012: 47 fig.1 for a comparison of dimorphism in humans and other apes and 50–58 for a discussion of its likely causes.Labuda et al.2010和Poznik et al.2013: 565描述了关于现代人当中一定水平的一夫多妻制的基因证据。Bowles 2006提出了繁殖性的矫正在人类利他主义行为演化中的作用。
[4] Shoulder: Roach, Venkadesan, Rainbow, and Lieberman 2013.Fire: Marean 2015: 543,547.Stone tips for projectiles: Henshilwood et al.2001; Brown et al.2012.Boehm 1999:174–181 attributes considerable leveling effects to these developments, most recently followed by Turchin 2016b: 95–111.See also Shultziner et al.2010: 329.Language: Marean 2015: 542.Boehm 1999: 181–183, 187–191 emphasizes the equalizing potential of language and morality.Timing: Boehm 1999: 195–196, 198, with a preference for relatively recent and sudden changes, whereas Dubreuil 2010: 55–90 and Shultziner et al.2010: 329–331 give greater weight to earlier changes.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智人化石遗迹可以追溯到大约19.5万年前:McDougall, Brown and Fleagle 2005。这与Elhaik et al.2014的现代DNA研究指出的,大约超过20万年前的物种形成时期是一致的。
[5] 这一表述通常指的是从大约30万年以前一直到农业生产的出现这一段时间。
[6] Material constraints: e.g., Shultziner et al.2010: 327.Leveling needed to combat natural hierarchies: Boehm 1999: 37, 39.Enforcement: Boehm 1999: 43–89; also, more briefly,Shultziner et al.2010: 325–327; Kelly 2013: 243–244; Boix 2015: 46–51; Morris 2015: 33–43.
[7] Marlowe 2010: 225–254, esp.232–234, 237–238, 240–241, 248, 251–254.Typical character(on the Hadza as “median foragers”): 255–283.The !Kung bushmen are another wellknown and much-cited case: Lee 1979; 1984.
[8] Growth and surplus: Boix 2015: 54–55 for the point about heterogeneous outcomes.Low inequality: Smith et al.2010b, and see herein, pp.37–39.
[9] Outside contacts: Sassaman 2004: 229, 236–238.Not “living fossils”: Marlowe 2010: 285–286; and Kelly 2013: 269–275 on hunter-gatherers as a proxy for prehistory, a complex yet useful analogy.
[01] 1英里=1609.344米。——编者注
[10] Trinkaus, Buzhilova, Mednikova, and Dobrovolskaya 2014 is now the authoritative treatment of the Sungir finds: see esp.3–33 on the site, date, and mortuary behavior and 272–274, 282–283, 287–288 on the injuries and disorders.Bead size: Formicola 2007: 446.Inherited status: Anghelinu 2012: 38.
[11] Vanhaeren and d’Errico 2005; Pettitt, Richards, Maggi and Formicola 2003; d’Errico and Vanhaeren 2016: 54–55.
[12] See esp.Shultziner et al.2010: 333–334; Anghelinu 2012: 37–38; Wengrow and Graeber 2015.Marean 2014讨论了适应沿海生活的悠久历史和重要性。
[13] 关于西海岸的一般情况,现在可以简单参考Boix 2015: 98–101; Morris 2015: 37。实际上,因果关系可能更为复杂:e.g., Sassaman 2004: 240–243, 264–265.Kelly 2013: 252–266,esp.251 fig.9.3, offers a general model.Aquatic foragers: Johnson and Earle 2000: 204–217,esp.211–216。
[14] Prentiss et al.2007; Speller, Yang, and Hayden 2005: 1387 (Keatley Creek); Prentiss et al.2012,esp.321 (Bridge River).
[15] Flannery and Marcus 2012: 67–71 (Chumash).Complexity: Kelly 2013: 241–268, esp.242 table 9.
[16] Chronology of domestication: Price and Bar-Yosef 2011: S171 table 1.关于农业起源的问题,特别要参考Barker 2006和Current Anthropology专刊的一些文章52, S4 (2011),S161–S512。Diamond 1997依然是关于驯化的范围和步骤的全球变化的最简单直接分析。Nonlinearity: Finlayson and Warren 2010.
[17] Natufians: Barker 2006: 126; Price and Bar-Yosef 2010: 149–152; Pringle 2014: 823; and cf.also Bowles and Choi 2013: 8833–8834; Bowles 2015: 3–5.
[18] Impact of Younger Dryas: Mithen 2003: 50; Shultziner et al.2010: 335.Pre-Pottery Neolithic: Price and Bar-Yosef 2010: 152–158.
[19] Rivaya-Martínez 2012: 49 (Comanche); Haas 1993, esp.308–309 tables 1–2 (North American societies).
[20] Borgerhoff Mulder et al.2009: 683 fig.1 (sample), 684 table 1 (43 wealth measures for these societies), S34 table S4 (inequality for different wealth types), 685 table 2, S35 table S5 (Ginis).在多米尼加受到限制的种植者中,较高的土地不平等程度提高了他们相对于觅食者的生存模式下的平均物质不平等程度,这就意味着这两个群体可能要比这个小样本所显示的更为一致。关于种植者的数据,参见Gurven et al.2010。
[21] Borgerhof f Mulder et al.2009: 686, with S37 table S7; Smith et al.2010a: 89 fig.3.
[22] Model: Borgerhof f Mulder et al.2009: 682.Correlation: Smith et al.2010a: 91 fig.5.Shennan 2011对于无形财富到物质财富资源的转移,以及它创造不平等的潜力给予很大的权重。
[23] Smith et al.2010a: 92 (defensibility); Boix 2015: 38 table 1.1.B (global survey); Bowles and Choi 2013 (property rights).后者开发出一个正式模型,其中,气候的改善使得种植业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可被预测,并且导致了农业的扩张和私有产权的出现。
[24] Wright 2014.
[25] Mesopotamia: Flannery and Marcus 2012: 261–282, esp.264–266, 268, 272, 274, 281.也参考对于埃兰(胡泽斯坦)一个有着超过1000个墓葬的墓地的分析,其中包括从富有铜制品和精美彩陶的墓葬到仅有烹煮锅罐的贫穷墓葬,也可以参见Price and Bar-Yosef 2010: 159对于幼发拉底河岸边哈陆拉村落遗址中100多个墓葬中不平等状况的研究。
[02] 1磅=0.4536公斤。——编者注
[26] Biehl and Marciniak 2000, esp.186, 189–191; Higham et al.2007, esp.639–641, 643–647,649; Windler, Thiele, and Müller 2013, esp.207 table 2 (also on another site in the area).
[27] Johnson and Earle 2000对社会进化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分析。关于典型的群体规模,参见246页表8。
[28] Global sample: Boix 2015: 38 table 1.1.C.North America: Haas 1993: 310 table 3.SCCS: Boix 2015: 103 table 3.1.D.
[29] Cereals: Mayshar, Moav, Neeman, and Pascali 2015, esp.43–45, 47.Agriculture and state formation: Boix 2015: 119–121, esp.120 fig.3.3.参考Petersen and Skaaning 2010对于在地理和气候特征影响下的驯化导致的国家形成上的时间差别的分析,这也支撑了Diamond 1997的研究。同样可以参考Haber 2012对于谷物储存在国家形成的后期阶段作用的分析。
[30] Quote: Haas 1993: 312.Scheidel 2013: 5–9 presents and discusses various definitions of the state, several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summary given in the text.For the nature of premodern states, see herein, pp.46–48.Maisels 1990: 199–220, Sanderson 1999: 53–95, and Scheidel 2013: 9–14 offer surveys of modern theories of state formation.
[31] Circumscription theory: Carneiro 1970; 1988.For simulation models of state formation driven by warfare, see Turchin and Gavrilets 2009; Turchin, Currie, Turner, and Gavrilets 2013.Boix 2015: 127–170, 252–253 also stresses the role of warfare.
[32] Decentralized polities: e.g., Ehrenreich, Crumley, and Levy 1995; Blanton 1998.Quote:Cohen 1978: 70; see also Trigger 2003: 668–670 for pervasive hierarchization.Values:Morris 2015: 71–92, esp.73–75, 92.
[33] Estimates: Scheidel 2013, conjectured from McEvedy and Jones 1978 and Cohen 1995: 400.On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state, see herein.For the structure an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s,see esp.Doyle 1986; Eisenstadt 1993; Motyl 2001; Burbank and Cooper 2010; Leitner 2011;Bang, Bayly, and Scheidel forthcoming; and the précis in Scheidel 2013: 27–30.For citystates, see esp.Hansen 2000 and, very briefly, Scheidel 2013: 30–32.
[03] 1平方英里≈2589988.11平方米。——编者注
[34] For the evolution of steppe empires—which are absent from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for want of relevant data—see Barfield 1989; Cioffi-Revilla, Rogers, Wilcox, and Alterman 2011; http://nomadicempires.modhist.ox.ac.uk/.Cf.also Turchin 2009 for their role in large-scale state formation.Growing size: Taagepera 1978: 120.
[35] Fig.1.1 from Gellner 1983: 9 fig.1 as reproduced in Morris 2015: 66 fig.3.6.
[36] On the nature of premodern states in general, see esp.Claessen and Skalník 1978b; Gellner 1983: 8–18; Tlly 1985; Giddens 1987: 35–80; Kautsky 1982, esp.341–348; Haldon 1993;Sanderson 1999: 99–133; Crone 2003: 35–80 (quote: 51); 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9: 30–109 and across-disciplinary meta-survey in Scheidel 2013: 16–26.
[37] Makers and takers: Balch 2014.Babylonia: Jursa 2015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嫁妆实际价值的中位数和均值分别高出70%和130%,同时这两个时期的基尼系数是0.43(n = 82)和0.55(n = 84),或者最高的异常值被从每一个数据集剔除之后分别是0.41和0.49。关于新巴伦的经济动态,参见Jursa 2010。
[38] For regressive distribution in despotic regimes, see, e.g., Trigger 2003: 389 and Boix 2015:259.Winters 2011追溯了历史进程中的寡头权力,主要聚焦在财富的保护上(特别是20~26页)。互惠的观念主要存在于概念领域。Claessen and Skalník 1978a: 640优美地定义道:“早期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在一个——至少被分成了两个基本社会阶层或新兴的社会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者关系的特征是前者的政治主导性和后者的进贡义务并存的——复杂、分层社会中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制,那种互惠性是基本原则的共同意识形态使其合法化了。
[39] For Mamluk Egypt, see herein, p.82; for the Roman Republic, herein, pp.71–74 and chapter 6, p.187.
[40] Entrepreneurs: Villette and Vullermot 2009.For the Roman Republic, see herein, p.73; for France, pp.83–84.我参考个人化的政治喜好,是为了把这些因素与减税的作用区分开。在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最高收入群体所占比例有所上升,这些人整体上受益于富人。
[41] For the role of returns on capital and of shocks on these returns, see esp.the concise expositions in Piketty and Saez 2014: 841–842; Piketty 2015b: 73–78, and more generally Piketty 2014: 164–208.For the debate, see herein, chapter 15, pp.411–423.
[42] Hudson 1996b: 34–35, 46–49; 1996c: 299, 303; Trigger 2003: 316–321, 333; Flannery and Marcus 2012: 500–501, 515–516.苏美尔人的经验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代表了这些过程最早的得以保存下来的例子。
[43] Hudson 1996a: 12–13, 16; Flannery and Marcus 2012: 474–502, esp.489–491 on Lagash.For debt relief, see herein, chapter 12, pp.359–360.
[44] Ebla: Hoffner 1998: 65–80, esp.73–77.Quotes: 75 paragraphs 46, 48.The Hurrians were located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the Hittites in Anatolia.
[04] 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45] Foster 2016: 40, 43, 56, 62, 72, 90, 92; also Hudson 1996c: 300.Quotes: Foster 2016: 8(Rimush), 13 (Naram-Sin), 40 (scribes), 43 (elite).For the collapse of the Akkadian empire,see herein, chapter 9, p.280.在后续的帝国形成过程中,首都的精英和政府官员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例如Yoffee 1988: 49–52。
[46] Trigger 2003: 375–394 surveys these features across several early civilizations.For the Oyo,see 393.The contributions in Yun-Casalilla and O’Brien 2012 and Monson and Scheidel 2015 add up to a broad overview of fisc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
[47] 第一段引用来自所谓的巴比伦神义论,这是一个用中巴比伦语言写成的文本:Oshima 2014: 167, line 282,第二段来自Trigger 2003: 150–151。
[48] Quote: Fitzgerald 1926.For stature inequality, see Boix and Rosenbluth 2014: 11–14,reprised in Boix 2015: 188–194; and see also Payne 2016: 519–520.Scheidel 2009b surveys reproductive inequality across world history.
[49] See herein, p.48 (Babylonians), pp.76–77, and chapter 9, pp.267–269 (housing).
[50] See herein, appendix, pp.447–449 (distributions), chapter 6, pp.188–199 (Greeks), chapter 3,p.108 (America).洛伦茨曲线是用来描述给定人口中资产分布状况的图。少数成员的高度集中会引起曲线右端的急剧上升。
[51] Oded 1979: 19, 21–22, 28, 35, 60, 78–79, 81–91, 112–113.See also herein, chapter 6, p.200.
[52] Regarding slavery, see esp.Patterson 1982: 105–171 on the different modes of creating and acquiring slaves, Miller 2012 for slavery in global history, and Zeuske 2013 for the global history of slavery.For Rome, see Scheidel 2005a; for Sokoto, Lovejoy 2011;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 p.108.
不平等有很多来源。生产性资产的本质和它们被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方式,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剩余的规模和商业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都以一种复杂和不断改变的方式相互作用以决定物质资源的分配。调节这一相互作用的机构对于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使用,以及对最终根植于动员和使用暴力的压力及冲击高度敏感。以稳定且陡峭的层级结构,以及至少从前工业革命的社会标准看,在例如获取能源、城市化、信息处理和军事能力这些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得分很高,规模非常大的,同时也维持了很多代的农业帝国,在相对较好的免遭显著的暴力冲突的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关于不平等动态的观察。从最后这一方面来看,它们代表了与相对和平的19世纪,即一段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西方世界最接近的情况。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古代帝国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意义上,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果。这些相隔1500年或者更久,以及除了秩序、稳定和受保护的发展这些共同经历外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不同文明,都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保持了巨大的差异。穿过时间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大的暴力性冲突的缺位一直是高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 [1]
我提供两个案例研究来表明这些前提:中国汉朝和罗马帝国,它们每一个在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都掌握了大约1/4的全球总人口。古罗马被贴上的标签是“一个完全通过获得土地创造出财富的产权帝国”,中国汉朝时的财富是凭官位而不是私人投资获得的。这种对比看起来有点夸张:在这两种环境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如影相随地纠缠在一起,都是收入和财富的关键来源,也就成为物质不平等的有力决定因素。 [2]
紧随短暂的秦王朝(它最先统一了更早时期的“战国诸雄”)之后建立起来的汉王朝,是一个统治期超过400年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性大帝国,它保留了有关收入和财富集中动态变化情况的丰富证据。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来自谁来控制土地,土地上的剩余以及农村劳动力、创造和毁灭大量财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农业耕种的商业化是一个原因:根据汉朝的第5位皇帝,即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80—前157年)的一项记载,被迫以很高的利息率借款的小片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输给了商人和高利贷者,后者在佃农、雇佣劳动力或者奴隶的帮助下种植他们建立的大型庄园。 [3]
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系一种作为其财政和军事征募系统基础的小规模的农业主生产模式,力图限制这些压力。在公元前140—公元2年的11个例子当中,政府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地方精英阶层的成员被迫迁移到首都地区,这不仅是一种确保他们政治忠诚的方式,也是为了限制他们在地方层面的权力。在这一做法被暂停之后,富人和地位高的人通过购买或强占土地,以及压迫穷人的方式来积累资产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在公元前7年,经过很多代精英的侵蚀之后,宫廷中的最高顾问最终建议实施法律限制以对付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然而,这些本可以对精英所持有的土地和奴隶设定一个总体的上限,以及期望没收过多资产的措施很轻易地就被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阻挠了。不久之后,篡权者王莽设想了更有力的干预手段。后来,从土地国有化到奴隶贸易终结的各种宏伟的计划为他招来了各种敌对势力。当时规定,家庭应该放弃给定上限以外的所有土地,分给亲属和邻居。恢复那种公认的周期性再分配的古老传统(所谓的“井田制”),定期调整土地所有权被当成确保公平的关键之举,而售卖土地、房屋和奴隶的行为被禁止,否则将被判处死刑。毫不奇怪,这些规制手段(它们被真正尝试过,而不仅仅是由东汉的宣传所创造和美化出来的)被证明是不可执行的,而且很快被放弃了。当汉朝在地主支持下成功地东山再起时,这个新王朝很快就垮掉了。 [4]
汉朝的文献资料把通过市场活动的方式获取的财富,有偏向性地归结到商人那里,这是一个被政治上人脉深厚的文人群体蔑视的阶级,这些文人提供了我们现在的分析所依靠的这些文本。历史学家司马迁把富有的商人形容为一种“指挥穷人提供服务”的阶级,同时大量属于他们的财富也可以与最资深的帝国官僚所拥有的相媲美。帝国掌权者因此将私有的商业财富作为一个目标。商人要承受比其他行业的成员更高的税收。在公元前130年之后的几年中,汉武帝统治之下的财政干预变得更为激进了,他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军事动员计划以应对来自北面的匈奴。汉武帝建立了对盐和铁的国家垄断。通过这种做法,他不仅获得了原来被私营者拿走的利润,而且也保护了作为应征入伍者和纳税人的小土地所有者,使得他们免遭投资于不动产的商业资本所有者的替代。他也提高了对商业资产的年度税收。很多大富翁被认为已经被消灭了。为了与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保持一致,这些平等化措施与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后者平息之后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5]
对抗商业资本的集中及其不平等社会后果的措施最终依然没有成功,这不仅是因为政策制定的不连续性,最为重要的是,商人很明确地把他们获得的收益投资于土地,从而躲避国家的索取。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他们的策略是: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禁令也不能阻止他们:就像商人不能被有效地禁止购买土地,所以他们也能成功地规避加入官场队伍的禁令,一些富有的企业家或者他们的亲属甚至上升到有爵位的贵族地位。 [6]
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官府任职以及更普遍的与政治权力的中心紧密接近是获得大量财富的另一条主要的路径。高级官员从国君的礼物和封地中获利。采邑的主人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分配给当地家庭的人头税。大量的财富从皇帝的恩宠和腐败中获得:好几位帝国的宰相和其他高级官员都被认为已经积累了不逊于所有有记载的最大富翁的财产。在东汉后期,高级职位能够赚取大量钱财的本质已经开始反映在购买它们的价格水平上了。法律特权以不断增加的“慷慨”保护着腐败官员。在一定等级以上的官员,没有皇帝的事先批准将不会被逮捕,同样的保护措施也延伸到量刑和惩罚上。 [7]
除了把他们的新增财富投资于那些合法的渠道之外,人脉深广的人也发现很容易欺压和剥削普通民众。官员滥用他们的权力来占有公共土地或者从其他人手中进行抢夺。这种来源传递出一种默认的期望:不管是政府授予还是通过影响力和强迫来获得,政治权力都应该转化为土地形式的耐用的物质财富。长久以来,这些过程创造出一个由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和受宠者结成同盟和联姻的精英阶层。有钱人或者自己任职,或者与那些有官位的人联系在一起,政府官员以及那些与行使这些职责联系在一起的人反过来积累了更多的个人财富。 [8]
这些动态发展既可能有利于,也可能限制家族财富持有的延续性。一方面,达官贵人的子孙更可能追随他们的脚步。他们和其他年幼的亲戚可以自动获得进入官场的资格,从用来填补官位的举荐系统中不成比例地获益。我们听说有些官员当中,一些人的六七个兄弟和子孙(在一个例子中,有不少于13个)也担任了帝国的行政官员。另一方面,掠夺成性和反复无常的政治权力的行使,即公职人员成为门阀,也逐渐破坏了他们的成果。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灌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在他的老家拥有如此之多的土地,对这种显赫地位的普遍厌恶让本地出现了一首童谣:
颍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
这首歌谣捕捉到了政治性财富岌岌可危的命运:多半是这样,爬得越高的家族摔得越狠。这种风险延伸到这一地位金字塔的最顶端——外戚家族。 [9]
更为系统性的清洗异己情形也发生在不同的精英层级中。汉朝的创立者把165位追随者封为贵族,并且给予他们采邑的头衔和收入,这是一个由不同家族逐渐垄断了高级政府职位和大量土地的集团。在汉武帝统治的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彻底褫夺了头衔和属地,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他的曾孙汉宣帝统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最有名的功勋卓越的将领的后代都以雇工,或者其他仆从的身份进行工作。
汉朝早期的顶层精英因此没有持续存在超过一个世纪,随后就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家族的残留一起被清除了。新的宠臣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一个世纪之后,篡位者王莽也热衷于打倒和驱逐他们的后裔,而他自己的支持者相应地也被东汉王朝的追随者取代了。结果是,在公元1世纪的末期,只有少数西汉的贵族家庭依然是存在的。 [10]
统治阶级中充斥着暴力死亡和私人财产的征收。无数的达官显贵被处以死刑或者被迫自杀身亡。《史记》和《汉书》中记载着关于“酷吏”的特殊章节,这些人按照他们皇帝的要求迫害统治精英阶层的成员。很多被盯上的目标都失去了生命,有时是整个家族都被根除了。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内部斗争同样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员变动和资产转移。在精英圈子中,这种持续的“搅动”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一些人获益,另一些人必须失去。暴力性的财富建设和再分配的动态变化对精英财富的集中施加了限制:一旦特定的家庭和群体与其他人的距离拉得太远,对手就会把他们推翻。 [11]
然而,尽管这样阻止了极少数超级富裕的,而且可能在长期保持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的家族的出现,看起来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以大众为代价不断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攻击性的政权干预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同时,处于上升期的东汉王朝为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打下了基础。20个汉朝诸侯王,即统治者近亲的采邑中拥有的家庭数量,从公元2年的135万户上升到公元140年的190万户,分别相当于帝国人口统计中登记的所有户数的11%和20%。尽管随着整个家族被屠杀或者被流放,暴力性的派系冲突不断夺走生命和家庭财富,富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新的秩序中获得了收益。由于在帮助汉室重新掌权中发挥了作用,大地主家庭使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且通过债务使得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对其臣服。这一时期的一些资料指出,这些精英在人口统计中作假以隐瞒应税财产。登记的家户数量从公元2年的超过1200万户下降到公元140年的不足1000万户,当时是帝国南部不断扩张的殖民时期,因此,地主将自耕农转变为无地的佃户,并且抵制国家执法人员干预,至少部分反映了不断恶化的违规行为。 [12]
在东汉王朝的统治下,一个更稳定的帝国精英阶层看起来已经形成了,使得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上升到高等级被认为是非比寻常的事情。这种统治阶级门槛的封闭与越来越多的案例一致,即家族在培养高级官员方面的突出地位持续了六七代之久,这使得一些家庭长期拥有过度的代表权。尽管有持续的内部斗争和再循环,我们还是观察到一种更为持续的权力和财富集中的潜在趋势。这一过程伴随着更有凝聚力的精英阶层的形成,新的精英阶层对公务任职的依赖减弱。财富的私有化最终达到了能够负担更多的保护以对抗掠夺性干预的水平,即使日益缩小的国家权力使得政府的职位不那么重要。同时,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两极分化看起来加剧了,后者进入各种从属性的安排当中,不再仅仅只是契约性义务了。在帝国解体之后,佃农演变成强大的地方领主(地主)的家仆。依赖性的租佃制度导致了支撑私人军队的庇护主义。在公元3世纪,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挑战权贵了。 [13]
汉朝维持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业投资者组成的精英阶级,这些群体的成员有着明显的重叠,并且在他们中间,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存在着资源的竞争。从长远来看,首要的趋势是随着国家对于自给的生产者的控制弱化,以及租金被挤出了税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程度不断上升。那些有名望的家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有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变得更加强大。统治者对待精英的方式从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军事性领导转变为汉朝时的调和性政策,这种政策取向只是零星地被激进的统治者的干预行为打断。汉朝的复辟使得权力的重心进一步地转向富有的精英。这种不平等的演化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段延长的,允许以小片土地所有者,最终甚至是以国家统治者为代价的财富集中的和平时期,以及正在进行的对精英阶级成员所获得收益的掠夺性再循环。前者增强了不平等,而后者削弱了它。然而,到东汉后期和公元3世纪,财富集中已经大获成功。
汉朝的经验仅仅是对中国不平等历史的定义性特征的首次重复。区隔开主要朝代的暴力动乱注定会减少一些既存的经济差异。新政权实施的土地再分配应该会有助于这一矫正过程,但是通常会让步于再次发生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就如同在隋朝(581年)、唐朝(618年)、宋朝(960年)和明朝(1368年)发生的那样。在每一个新的王朝,作为新的支持者的精英人士都被置于结合政治影响和个人财富的位置上。在唐朝末年,贵族阶级被打倒,即我在第9章描述的一种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源。少数有名望的家族能够在两三个世纪的时间中维持权力,享受着高级职位的特权,而且集聚了巨大的财富。贵族、官僚和功名持有者通常被免除了税收和劳役,这就进一步地加速了他们手里的资源集中。他们再次以国家所有的土地为代价实现了私有土地的扩张,地主也再一次使得在他们控制下的农民家庭从税收登记中消失了。
在这一阶级遭遇戏剧性的毁灭之后,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在宋朝的统治下产生了。统治者的馈赠创造出大型庄园,后来为农民提供政府贷款的各种努力也很快止步不前了。在南宋王朝的统治下,土地集中和官官相护更加严重;迟来的为地产规模制定上限的尝试遭到精英阶层的敌视。蒙古入侵者慷慨地奖励首领土地所有权,同时为他们的普通士兵实施了养老金制度。在蒙古地主和官员被明朝军队驱逐之后,新的王朝建立者朱元璋发放了大量的地产给他的追随者,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后来,他和他的继任者试图减少这些人财产的一些尝试都失败了。相反地,由于帝王赏赐、购买、强行侵占和嘉奖(农民将土地割让给富人以逃避国家的税收),精英阶层的资产增加了。一个对16世纪起源的精辟总结就是:扬子江以南,穷人和富人相互依靠,弱者都转让了他们的土地。
人口普查的弄虚作假隐藏了精英持有资产的真实情况。再一次地,政府资产成为获得财富的路径之一,《大明律释义》直言不讳地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许多有功之臣将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大规模地获得土地和豪宅,以及占有人口。
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能够追溯到1500年以前东汉的几种过程的一次重演:
在明朝末期,上层阶级以世袭臣服的方式掌握了数量庞大的农奴。在县一级,已经几乎没有自由的平民了。此外,如果主人的权力不断变弱,他们将会不受约束并离开。有时他们甚至会反叛,夺走他们主人的田地,夺取他们主人的财产,以及将他们的忠诚转移到一些刚刚获得地位的其他人身上。原来的豪门可能会为此进行上诉,但是当权者可能会仅仅以谁是强者为基础来处理这一案子。 [14]
最后,清朝将大量的明朝土地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宗室和其他人,也被多种多样的税收腐败阴谋困扰着。官员通过伪造欠款来隐瞒贪污;夸大自然灾害的规模来要求免税;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虚报贫瘠的状况;从富人那里借钱预付税收;偷钱,然后把债务当作平民的应付欠款;重新划分土地但还是以过去的比率征税,从中赚取差额;扣留或伪造收据。贵族阶层和退休的官员常常根本不纳税,一些现役的官吏把这一负担转嫁给平民以换取分一杯羹的机会。最后,土地被登记在多达几百个假名字之下,这就导致由于太麻烦而无法追查一些小额的应付欠款。高级官员的腐败是财富积累的一个标准机制,等级越高就越多。根据一项估计,官员的平均总收入达到了他们薪水、奖励、津贴的官方合法收入的12倍,但是对总督而言,这将会远超过100倍,对和珅这位18世纪下半叶清廷的首辅来说,则高达40万倍。处决和没收财产是实现公平的永恒对策。 [15]
但是,让我们再次回到古代世界的“最初的1%”。罗马帝国不平等的演化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的相似,从文本到考古遗址,这些证据上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使得我们可以更详尽地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并且把它与帝国的兴起和统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一旦罗马将其权力投射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并且越来越多地进入地中海东部这些希腊王国的财富之中,量化的信息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有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见表2.1),贵族财富的规模也极大地增加了。 [16]
表2.1 罗马社会中最大已知财富的发展和罗马帝国控制的人口数量: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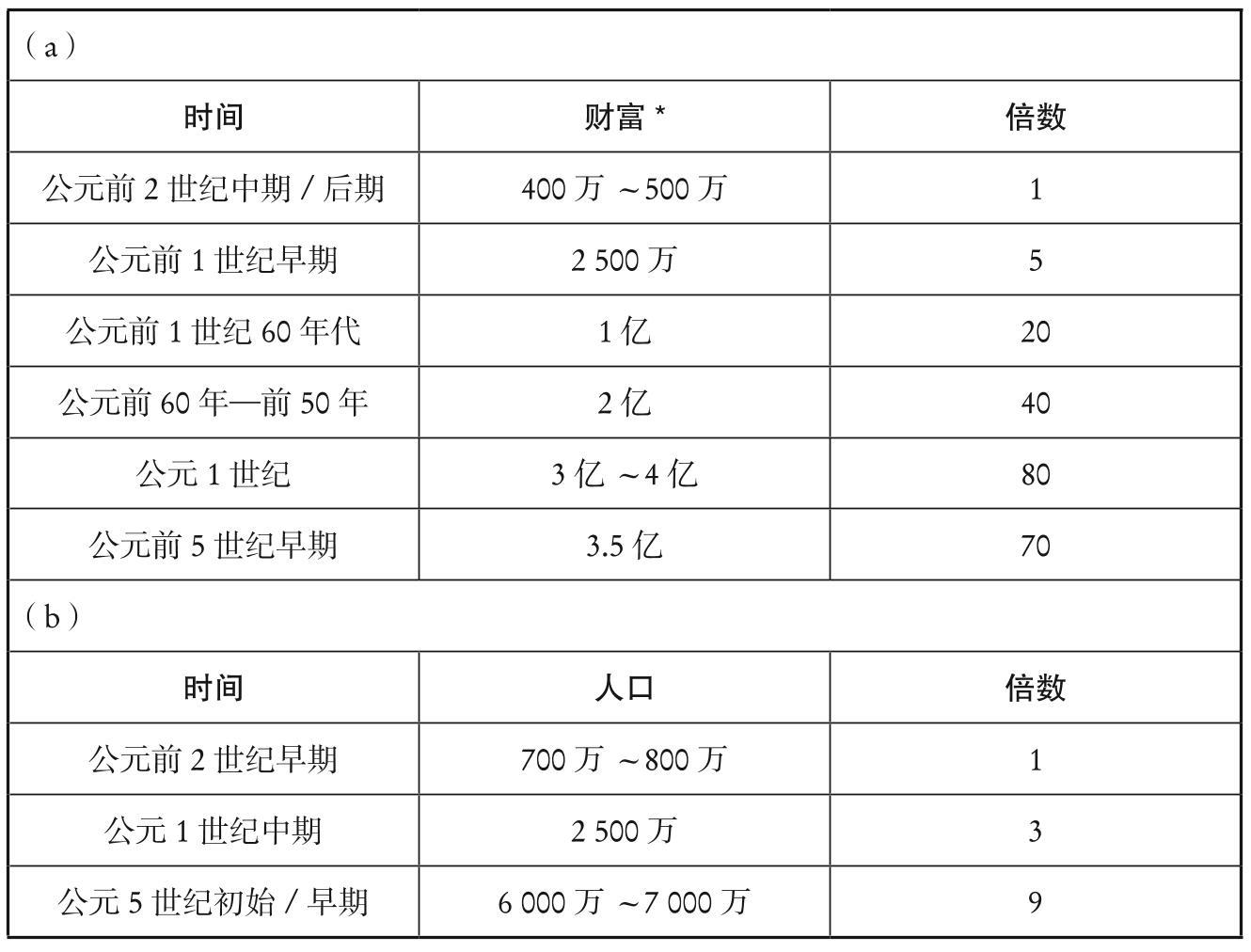
*以帝国时期的货币塞斯特斯表示。
这些数字表明,在超过5代人的时间里,私人财富的上限已经上升了40倍。在最保守的假设水平上,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治理国家的元老院阶级控制的总财富上升了一个量级。通货膨胀一直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迹象表明普通市民中的平均人均产出或者个人财富能够以超过上层阶级财富所经历的比例增长。罗马帝国的权力群体因而变得非常富裕,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相对意义上:元老的财富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罗马统治下的从地中海盆地到其内陆在人口数量上的同期增长。同时,精英的富裕也进一步扩展到罗马社会当中。在公元前1世纪,至少10000个,以及也许有这个数字的两倍多的大多在意大利本土的公民,在财富上明显达到了40万塞斯特斯这一骑士阶层成员的统计门槛,骑士阶层是元老院阶级之后的第二高的等级。考虑到仅仅是几代以前,达到几百万的个人财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就表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下游也享受了可观的收益。普通公民中的这些趋势依然比较模糊,但是也可能已经受到了两种不平等力量的影响:强烈的城市化,这通常趋向于恶化不平等;以及在意大利一处就有100多万人沦为奴隶,这些人被合法地剥夺了所有私人财产,同时大多数人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收入,因而我们能够预计这会扩大整体社会的经济差异。 [17]
所有这些额外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植根于市场关系的经济发展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阶段确实上升了。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中使用奴隶,以及关于出口红酒和橄榄油的丰富考古证据,都表明罗马的资本所有者的成功。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可能的供给和需求规模的简单估计表明,土地所有权和相关的商业活动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收入,使得罗马贵族像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富裕。实际上,我们的资料强调的是强迫劳动作为最高等级群体收入和财富的一种来源的最重要意义。大量财富从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中获得,罗马式治理非常有利于进行剥削。省级政府机构是暴利的,同时寻租行为只是受到了法律和用来起诉敲诈勒索的法院的较弱约束,当权者中的联盟构建和租金分享提供了对抗起诉的保险机制。此外,在罗马的年利率普遍达到6%的时期,富有的罗马人对各个省会城市施加了高达48%的利率,这些城市急需金钱来满足其总督的需求。骑士阶级的成员从广泛的农业税的实施中获得了收益,在特定省份收取一定量的税收的权力被拍卖给了财团,然后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它变为利润。战争也是精英收入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来源。罗马指挥官对战利品拥有完全的权力,并且决定了如何将战利品在来自精英阶层的军官和副手、国库和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割。基于战区和战争的数量,据估计,公元前200年—前30年,3000多位生存在这一时期的元老中,至少1/3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 [18]
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罗马共和国的系统进入持续半个世纪的不稳定状态,暴力性的内部冲突通过强迫性地对现有精英财富的再分配创造出新财富。那时,超过1600名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元老和骑士被放逐,这是一种政治驱动的定罪形式,使得他们失去了财产甚至生命。胜利者阵营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中抢购贬值的充公资产而获利。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更为持久的内战期间,暴力性再分配加速了。在公元前42年,另一轮权力剥夺消灭了超过2000个精英家庭。从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新人的地位得以上升,罗马的上层社会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逆转。主宰了这个舞台几个世纪的家族最终随着被其他人取代其位置而垮台。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它开始表现出一些君主政体的典型特征,正如我们刚才在汉朝的例子中相当详尽地观察到的,包括精英阶层从血腥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受益或者受损,以及政治原因所导致的精英财富的非连续性。 [19]
共和国的衰落带来了保留着共和制机构这些外在装饰的永久性军事独裁制度的建立。大量的财富现在从周围流向了统治者(皇帝)和宫廷。公元1世纪的时候,一些资料显示:有6个人的财富介于3亿~4亿塞斯特斯,这要比共和国时期所知的任何例子中的数量都要多。财富由这些宠臣逐步积累起来,但大多数最终都被财政吸收了。精英财富的再循环可以采取很多形式。贵族的盟友和受宠者经常期望把统治者包含在他们的遗嘱之中。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自称,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他朋友的遗产中获得了14亿塞斯特斯。在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下,罗马的年鉴记录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由实际发生或想象中的背叛行为和阴谋带来的处决案例,以及对精英财产的充公事例。罗马社会上层中有记载的或者隐含的充公规模,大约是一些皇帝统治期间精英财富总额的几个百分点的水平。这说明了富人间暴力再分配的残酷。归根结底,赏赐和收回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统治者是根据政治计算来创造或者撤回精英的财富。 [20]
在独裁统治之下,更多传统的政治性致富手段的类别持续存在着。各省的总督现在从其提供的良好服务中可以获得每年100万塞斯特斯的报酬,但他们依然暗地里榨取大量的财富:一位总督进入叙利亚领域时还只是一个“贫民”,但两年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富豪”了。一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南部的总督在他的信件里面不明智地吹嘘说,他已经从他的居民中敲诈了400万塞斯特斯,甚至把他们其中一些人转卖为奴隶。在这一食物链的更底端,一位监督着高卢的帝国国库的皇帝奴隶掌管着16个低等级奴隶,其中2个奴隶负责照看他明显过多的银器。 [21]
帝国的统一和连通性促进了个人财富的扩张和集中。在尼禄的统治之下,直到他夺走他们的财产之前,有6个人被认为掌握了非洲范围(以现代的突尼斯为中心)的“一半”财富。尽管明显比较夸张,但这种说法并不一定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在这个地区,大片地产可以被形容为与城市领土大小相匹敌。最富有的外省人加入中央帝国的统治阶级当中,迫切希望得到地位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充分利用它们提供的机遇来进一步获得财富。对罗马文献的总体研究发现,富豪的不同称谓几乎完全被应用于具有执政官地位的元老,他们享有最有利和最好的获得更多财富的途径。正式的地位排序是根据财务能力进行的,同时统治阶级的三种等级的成员资格——元老、骑士和十人长是与错开的统计门槛捆绑在一起的。 [22]
个人财富和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在地方层面也得到了忠实的“复制”。成熟的罗马帝国包括大约2000个大体上自治的城市或者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区,这些社区处于流动的总督、精英官员的少数骨干、帝国自由民和奴隶的松散监管(以及伺机敲诈)下,这些人最为关心的是财政收入。每一个城市通常都是由一个代表本地富有精英阶层的委员会管理的。这些机构,其正式成员是由这些十人长构成的,他们主管的不仅有本地税收和支出,还有为国家评估他们社区的财富,同时他们还有责任筹集资金交给收税员和包税人。如果关于这一时期的慷慨的市政支出的考古和碑文证据是比较可靠的,那么这些精英知道如何从遥远的帝国中心手中保护自己的资产,并且将大量的剩余留存在本地,或者放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于维持公共设施。 [23]
本地财富的逐渐集中在所有罗马城市中最广为人知的那一个遗址上得到了很好的反映,那个遗址即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灰烬掩埋的庞贝。除了大量铭文提到的官员和进行生产的所有者之外,毁灭发生时的大多数住宅留存下来了,有时我们甚至可以识别特定建筑中的居民。庞贝的精英阶层包括享有进入本地政府机构特权的富有公民的内部核心成员。在城市结构当中,也是可以看见分层的。这座城市里面有大约50座带有宽敞的天井、柱廊庭院和多个餐厅的豪宅,还有至少100个低档一点的住宅,这些住宅的档次门槛降到一位市议会成员的已知最小的住宅的水平。这与从文本资料中所知的“存在大约100个精英家庭”的信息十分匹配,也许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只有部分人属于管理委员会。一般而言,在一个30000~40000人的社区中(包括这个城市属地),100~150个精英家庭和华丽的城市住宅就将代表了本地社会前1%或者2%的群体。这些家庭将城市范围内的农业庄园与城市的制造业和贸易结合在一起。这些精英的宅邸常常也包含商店和其他商业用房。
城市的不动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这种趋势是特别显著的。考古调查已经揭示出,所有这些大房子和很多属于第二等级的建筑都是通过吸纳几家之前比较小的住宅产生的。随着时间推移,相对比较平均的住房分配(因此可能也包括财富)与公元前80年罗马退伍老兵的强制安置相关,逐渐地让位于日益拉大的不平等,且大多以被排挤出城市结构的中等家庭为代价。作为一种大规模动员的军事文化,自上而下的再分配被稳定的独裁统治取代,两极分化也就随之而来了。较高的死亡率和可分割的遗产无法使资产分散,使社会结构金字塔扁平化,资产仅能用来在精英圈子中进行财富的再循环。 [24]
罗马帝国住房的考古数据更普遍地表明了罗马统治下社会分层的强化。如同我在第9章中会更详细讨论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北非的住房大小分配比这之前更不平等。同时,依赖于我们选择的数据集,同样的结果对意大利自身而言也是成立的。这并不奇怪,尽管帝国为那些位于或者靠近权力天平的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它同样也有利于更大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在君主制度统治的前250年间,从历史的标准看,破坏性的战争和其他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帝国的和平环境为资本投资提供了保护性的外壳。除了那些处于非常高位置的人,有钱人对于持有和传递他们的财产还是相对放心的。 [25]
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强化的分层社会,其中最富有的1%或者2%的人吸收了生计最低限度之外的大量可用剩余。至少粗略量化罗马帝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可能的。在它公元2世纪中期的发展巅峰,这个大约有7000万人的帝国生产出来的年度GDP接近于5000万吨小麦等价物,或者接近200亿塞斯特斯。相对应的人均GDP为800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这看起来与其他前现代经济相比也是合理的。根据我自己的重构,大约600个元老的家庭,20000位或者更多的骑士,130000个十人长,以及另外65000~130000个没有等级的富有家庭合起来,总计25万个家庭拥有的总收入应该在30亿~50亿塞斯特斯之间。在这个情景中,大约1.5%的家庭拥有1/6~1/3的总产出。这些数字可能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实际份额,因为这是从估计的财富的推定回报中获得的收入数据;政治租金将会使得精英的收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尽管地位低于精英圈子的人群的收入分布甚至更难以评价,一种保守的假设范围指向的是,对整个帝国而言,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4~0.45之间。这个数字要比它看起来的高得多。因为除去税收和投资之后的人均GDP仅仅是最低生活费用水平的两倍,估计出来的罗马帝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并不是远低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实际可能达到的最大值,这是一个很多其他前现代社会共享的特征。按照可以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提取的GDP比例来衡量,罗马帝国的不平等是极端严重的。除了富有的精英阶层之外,最多只有1/10的人口能够享受大大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 [26]
上层阶级的收入如此之多,以至要拿出一部分进行再投资,从而再一次加剧了财富的集中。权力的不对称可能迫使一些外省人把他们的部分土地卖掉以支付税收,这是一种我们甚至还不能开始量化,但是会有助于解释出现在后来一些世纪中的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跨区域网络的做法,这就带来了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将是否或者何时会触碰到天花板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准备把多大的权重放在公元420年以来的一个显然有些夸张的描述上面。埃及的历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把这些神奇的财富归功于罗马贵族的主要家族,据说“许多”贵族每年从他们的土地中获得4000磅黄金,其中的1/3是以实物偿付的,而那些在第二等级的人每年可以获得1000或者1500磅黄金。转换为早期君主统治时期的货币,上层的5333磅黄金的收入等同于公元1世纪时的大约3.5亿塞斯特斯,毫不逊色于当时所报道的最大的财富。看起来对最顶层的群体来说,财富的“高原”最早随着公元纪年开始前后君主制的创立而出现,虽然有一些波动,但一直持续着,直到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权力最终在公元5世纪彻底衰落。 [27]
同时,一些迹象表明,随着传统的城市精英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平等可能在本地和区域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富有精英阶层被分化为少数人,这些人受益于上层团体成员,而大部分人没有受益。这一过程的一些最好证据来自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晚期。现存的纸草文件说明了已经确立的、持续到公元4世纪的城市统治阶级是如何随着一些它的成员被拉走而逐渐削弱的,这些成员是因反对从地方财政义务中带来豁免的政府官员职位和提高个人致富的机会而被拖走的。在公元6世纪,这种向上的流动性似乎已经在埃及形成了一个新的、控制了大量可耕种土地和区域的关键位置的地方性贵族。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埃皮翁思家族,这是一个起源于十人长地位的家族,但它的一些成员控制了部分最高级的政府职位,并且最终控制了超过15000英亩具有很高生产力的土地,其中有很多都集中在埃及的一个单独区域当中。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公元323年的意大利,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在一个单一城镇中控制了超过23000英亩的土地。超级富豪像触手一样发散的土地持有已经扩展到帝国的很多地区,因此社群和地区水平上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 [28]
另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过程,促进了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在后来的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我们知道农民寻求有权力的地主(以及官员)的保护,后者承担了代表农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责任,最著名的是帝国的税务人员。在实践中,这干扰了财政收入的收集,并且强化了地主对于农业剩余的控制。这不仅反过来弱化了中央政府,而且把财政负担转嫁到了不那么强大的团体上,对中产群体伤害很大。再一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中国汉朝末年一样,私有军队和初期的军事割据并不会相距很远。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分层和物质不平等好像已经在整体上变得更加极端化了。早先这里可能还存在的中间地带已经被在强大的政治精英中进行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挤压了。罗马城和帝国的西半部被日耳曼首领夺取之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不平等可能甚至在持续地上升,一直达到公元1000年前后对拜占庭帝国估算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水平。伴随着它的特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交错,以及它所培育出来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帝国在被证明为不平等的永不休止的引擎上贡献的也就越多。 [29]
在它们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和罗马帝国共享着同一种造成了较高不平等水平的剩余占有和集中的逻辑。帝国统治导致资源流动,从而能够以一个在较小的环境中所不能想象的规模使得站在权力杠杆上的那些人变得富有。因此,不平等程度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所形成的帝国的绝对规模的一个函数。建立在几千年前首次发展出来的资本投资和剥削的机制之上,这些帝国把利益提得更高了。政府机构那里将会有更大的利润,降低贸易和长期投资的交易成本使得那些有多余的钱的人获益了。最后,只有通过征服、国家灭亡或者大规模的系统崩溃——所有这些本质上就是暴力性的动乱,帝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才能被终止或者逆转。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记录中缺乏防止根深蒂固的帝国不平等的和平方式,也很难看清楚任何能够从这些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生发出来的策略。然而,即使帝国崩溃,也往往只是一次重置,为另一波的放大和两极分化开辟了道路。
因为不平等能够被限制在完整的帝国政体之中,它是依靠精英群体内部资产的暴力性再循环实现的。我已经提到了埃及马穆鲁克的例子,其中这一原则可能以其最纯粹的历史记录的形式得以体现。在苏丹,埃米尔和他们的奴隶士兵分享着征服的收益:他们形成了一个在种族上分化和空间上分割的统治阶级,致力于从臣服的土著那里抽取租金,如果收益数量不能满足期望,这些土著可能就会受到摧残。在这一阶级内部持续不断的权力争夺决定了个人收入,同时暴力性的冲突常常改变这些分配。本地的产权所有者因面对敲诈勒索的威胁而寻求庇护,这就使得他们将其资产的责任让渡给来自马穆鲁克阶层的强人,并且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免被征税的资格。这是一种得到精英支持的做法,后者从中得到了自己的份额。统治者的回应则是不断诉诸对精英财富的彻底没收。 [30]
成熟的奥斯曼帝国完善了更为复杂的强迫性再分配策略。4个世纪以来,苏丹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处决了几千名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在14世纪和15世纪发生的征服战争的初期,贵族阶级已经作为武士家族与奥斯曼皇室形成联盟,后来又纳入其他地方的武士精英阶层。苏丹维护着自己的权威,15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专制主义统治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从奴隶中选择的出生低微的人才取代贵族家庭的后代成为官员。纵使这些家族继续竞争职位和权力,最终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对统治者而言,都被视为丧失了个人权利。政府职位变得不再有继承性了,同时官员的资产也被认为是受俸的,实际上变成了提供服务的附属物而不是私有财产。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在职期间获得的收益将会从他们的财产中扣除且被国库接收。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财产可能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被夺走,即任职和财富被视为不可区分。死亡时没收财产是清算和征收那些引起苏丹关注的现任官员的补充手段。精英阶层的成员试图尽其所能抵抗这种侵蚀,到17世纪,一些家庭已经成功地保持他们的财富达好几代人之久。在18世纪,随着政府职位和职责越来越多地被让出去,本地精英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就导致政府行政的广泛私有化,并且使得官员可以巩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中央政府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夺取资产,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战争压力下,再次征用财产,这引起了抵抗和逃离。1839年,当苏丹确保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奥斯曼的精英阶层最终以对其有利的方式终结了这场竞赛。至于包括罗马帝国和汉朝时的中国在内的其他帝国,中央政府控制统治阶级财富的能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削弱了。 [31]
在其他例子中,统治者要么太软弱,要么太遥远,从而无法干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集中。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既存的帝国的占领就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土地被授予贵族和骑士,然后他们有了对其居民的管辖权。西班牙征服者接着把这一做法推广到他们在新世界的领地,这里已经存在相似的做法了: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建立起将土地授给精英阶层、农奴和奴隶在内的强制性和攫取性制度。在墨西哥,西班牙征服者和后来的贵族很快夺取了大片的土地。直到被占据之后,这些土地才常常被追认为皇室的授予。埃尔南·科尔特斯在瓦哈卡的土地于1535年被要求限定继承权,这片土地在其家族手中延续了300年,最终包括15个别墅、157个印第安人村庄、89个大农场、119个大牧场、5个大庄园和15万居民。尽管有试图限制这种授予(被称为赐封)期限的皇家命令,它们却实际上都变成了永久性和可继承的财产,并且一个小规模的、超级富裕的地主阶级得以维持。大授地制操纵土著人变成债务奴隶以控制他们的劳动,反对关于强迫劳动的禁令。长久以来,这使得他们得以从最初杂乱无章的扩张行为和多样化的大授地制中开拓出更多长期的庄园,相关的农场由苦力进行耕种,他们在自留地和领地之间分配其时间。在地主的专制控制下,实际上形成了微型独立王国。后来的变化局限于上层社会,最为著名的是墨西哥在1821年的独立,导致了西班牙地主被驱逐并被那些大体上保留了现有制度的本地精英取代。土地所有制在19世纪期间甚至变得更加集中了,导致了第8章描述的革命。 [32]
秘鲁也发生了大致一样的事情,印加帝国同样把土地和收益授予精英家庭和高级官员。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军官最先被授予监护征赋权,同时他声称自己拥有分配土地和控制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的权力。大片土地以这种强制的方式被赏赐了,同时土著居民被赶到矿山之中,这都违反了皇家禁令。当皮萨罗拒绝对土地的授予施加上限并由此促使他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叛乱的时候,才产生了一些再分配。即便如此,土地和财富的集中甚至变得比墨西哥的更为极端了,大约500个领主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波多西的一些蕴藏丰富的银矿也被授予那些受宠的人,并且由附属的印第安人开采。本地部落首领通过让他们自己的村民提供工作服务与村民进行合作,作为交换,村民被任命为管理者,有时甚至得到他们自己的庄园。在典型的帝国模式中,外来和本地精英之间的合谋带来了经济两极化以及对普通大众的剥削。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像在墨西哥发生的一样,非法的占用变得合法化了,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的玻利瓦尔之后发生的土地再分配失败了,到19世纪,甚至土著人的公地也被吸纳进更大的庄园中。 [33]
权力精英能够保持住他们从政治职位或者政治联系中获得的财富。仅举一例,在近代法国,那些与王位最为接近的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响力变成在他们死后甚至是免职之后也能保留的巨大个人财富。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曾经担任国王亨利四世的高级部长及他的财政主管长达11年,一直到国王死时的1611年,其被免职之后依然生活了30年,留下了超过500万里弗,相当于那个时候巴黎27000个非熟练劳动力的年收入。红衣主教黎塞留从1624—1642年都担任着类似的职务,积累的财富有其4倍之多。然而,他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即任职于1642—1661年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使得这两人都相形见绌了,他挺过了1648—1653年的投石党起义期间的两年流放,依然还是留下了3700万里弗,相当于非熟练劳动力16.4万年工资的财产。权力较小的大臣也像强盗一样行事:黎塞留的盟友克劳德·德·比利翁,在他担任财政大臣的8年中获得了780万里弗;尼古拉斯·富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担任同一职务,在他于1661年被逮捕的时候,其财产的估值达到1540万里弗,尽管他的负债和资产一样多。将这些数字与最大的贵族财富进行比较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波旁王朝的一支,孔蒂王子的财富价值800万~1200万里弗。即使是最为激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控制后来的大臣时也仅是相对成功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特掌管法国国库长达18年才获得了相对比较微薄的500万里弗财富,而卢福瓦侯爵弗朗索瓦·米歇尔·泰利耶作为陆军国务大臣,工作了25年才积攒了800万里弗。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臣的收入从每年100万~200万里弗减少为接近几十万里弗。 [34]
我能够很轻易地添上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更多例子,不过基本论点是清楚的。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大的财富通常要更多归结为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实力。它们主要在持久性上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国家统治者的能力和实施专制干预的意愿来调节的。在社会最上层当中,强烈的资源集中和很高的不平等程度是确定的,尽管财富的流动性不断变化,对这些财阀圈子外部的人而言却几乎不相关。在首章中我们已经做了概略性描述,几乎所有前现代国家的结构特性都强烈支持一个特定的收入和财富集中的强迫–富裕模式,这种模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最大化不平等程度。结果,这些实体经常表现出来的是最大可能的不平等。如同我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所做的更详细的说明,对从罗马帝国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28个前工业化社会的粗略估计,得到一个77%的平均榨取率,这一比率是在给定的人均GDP水平上,理论上可行的最大收入不平等数量的实现比例。例外情况是很少见的:唯一合理的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在古代雅典的情况,直接民主和大规模军事动员(在第6章中进行了描写)的文化有助于限制经济不平等。如果基于有限的古代证据所做的现代估计可以信赖,那么公元1世纪30年代中的雅典人均GDP对前现代经济而言是相对较高的(可能是最低的生存水平的4~5倍,类似于15世纪的荷兰和16世纪的英格兰),市场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大约0.38的水平。根据前现代的标准,其中隐含的大约为49%的榨取率是格外温和的。 [35]
然而,雅典的这种异常现象并不能持续。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雅典最富有的人是赫罗德斯,他称自己是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和真正的宙斯的后裔。与他的血缘最近的家族是一个雅典贵族,其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上升到很高的公共职位,并且获得了大量财富,财富数量也许并不比罗马那些最富有的个体少很多。他的名字表明他与罗马那个最终产生了好几位皇帝的显贵的克劳狄家族存在关联。赫罗德斯的家庭甚至与罗马的上层阶级有着共同的典型经历,他祖父喜帕恰斯的财富(曾经被粗略估计是1亿塞斯特斯)被杜密善皇帝没收但在后来(有点神秘地)被返还了。赫罗德斯向许多希腊城市做了捐赠,并且赞助了公共建筑,最著名的是雅典的室外剧场。如果他真的拥有1亿塞斯特斯(等同于古典时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私人财富的24倍),从他口袋中拿出的年度资本收入就足以覆盖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时的雅典总政府支出(包括战争、政府、节日、福利、公共建设以及所有)的1/3,但他可能拥有甚至更多的财富。由于他是皇帝安东尼·庇护养子兼继承人的导师,赫罗德斯与皇帝的关系变得密切,在公元前143年,赫罗德斯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出任罗马帝国政府执政官的希腊人。帝国的恩慧和不平等占据上风。
[1] Morris 2010 and 2013对农业帝国中相对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做了观察。For the equivalence of preindustrial and early industrial inequality in both nominal and real terms,see herein, p.101 and appendix, pp.454–455.
[2] Wood 2003: 26–32提出了这一理想类型的对比。关于融合发展和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参见Scheidel 2009a; Bang and Turner 2015。在Scheidel 2016中,我提供了这两个帝国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
[3] 关于战国时期的改革和他们进行群众动员的文化,参考本书第6章。
[4] Ch’ü 1972: 196–199; Hsu 1980: 31; Loewe 1986a: 205; Sadao 1986: 555–558.Wang Mang:Hsu 1980:558; Sadao 1986: 558; Li 2013: 277.
[5] Merchants: Swann 1950: 405–464 (biographies); Ch’ü 1972: 115–116, 176; Sadao 1986: 576,578 (activities).Sima Qian: Ch’ü 1972: 182–183.For Wudi’s measures, see Hsu 1980:40–41; Sadao 1986: 584, 599, 602, 604.On the scale of his military efforts, Barfield 1989:54, 56–57; for his modernist policies in general, Loewe 1986a: 152–179.A second round of interventions was likewise rooted in violent turnover—namely, the usurpation of Wang Mang: Loewe 1986a: 232; Sadao 1986: 580, 606.
[6] Quote: Sadao 1986: 578 (Shiji 129); also 584 for manufacturers.Prohibition: Hsu 1980:41–42; Sadao 1986: 577.Overlap with landlords and officials: Ch’ü 1972: 119–121, 181.
[7] Nominal salaries were relatively modest: Scheidel 2015c: 165–174.Favoritism: Hsu 1980: 46–53.Size of fortunes: Swann 1950: 463–464.Sale: Mansveldt Beck 1986: 332 (for 178 CE).Protection: Ch’ü 1972: 96–97.
[8] Ch’ü 1972: 160–161, 175; Hsu 1980: 49, 54; Lewis 2007: 70.
[9] Ch’ü 1972: 94, 176–178 (continuities), and also 173–174 for specific families; Hsu 1980: 49(principle of rise and fall).
[10] On Wudi’s purges, see Hsu 1980: 44–46 (quote from Hanshu 16:2b–3b); Ch’ü 1972: 164–165; Lewis 2007: 69, 120.Eastern Han: Loewe 1986b: 275.
[11] Ch’ü 1972: 97, 184, 200–202, 212–213, 218, 226, 228, 237–243; Loewe 1986b: 276–277, 289;Mansvelt Beck 1986: 328–329.
[12] State intervention: Lewis 2007: 67 (on conscription).Fiefdoms: Loewe 1986b: 257, 259.Landlords and Han line: Li 2013: 295; Lewis 2007: 69–70.For failed reform attempts, see Ch’ü 1972: 204; Hsu 1980: 55; Ebrey 1986: 619–621.Census: Li 2013: 297.
[13] Ebrey 1986: 635–637, 646 (social closure, elite autonomy); Hsu 1980: 56 (retainers); Lewis 2007: 263 (clientelism); Lewis 2009a: 135 (magnates).
[14] Land redistributions: Powelson 1988: 164, 166, 168, 171.(Similar attempts, modeled on China, were made in Vietnam: 290–292.) For the Tang, see herein, chapter 9, pp.260–261.Song: Powelson 1988: 166–167.Ming: Elvin 1973: 235 (first quote), 236 (second quote), 240(third quote, from a text from around 1800 regarding Shanghai county).
[15] Schemes: Zelin 1984: 241–246.Income multiples and countermeasures: Deng 1999: 217–219.
[16] Shatzman 1975: 237–439 offers an exhaustive “economic prosopography” of the senatorial class from 200 to 30 BCE.For the early empire, see Duncan-Jones 1982: 343–344 and 1994:39; for the fifth century CE, see herein, p.78.The relevant individual fortunes are listed and discussed in Scheidel 2016.我根据后来的面值标准化了货币价值:1000塞斯特斯大概等于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的均值(关于人均GDP,参考Scheidel and Friesen 2009: 91)。
[17] For limited real income growth among commoners, see Scheidel 2007.The population figures are rough guesstimates.Equestrians: Scheidel 2006: 50.For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see herein, p.93.Slaves: Scheidel 2005a.
[18]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most recently, Kay 2014.Estimates of income sources:Rosenstein 2008, preceded by Shatzman 1975: 107, who observed, “It is obvious that income from agriculture was negligible in comparison with profits accruing from a senatorial career.” Income of governors, lenders, and tax farmers: Shatzman 1975: 53–63,296–297, 372, 409, 413, 429–437.Warfare: 63–67, 278–281, 378–381.Tan forthcoming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elite incomes and the fiscal system of this period.
[19] Shatzman 1975: 37–44, 107, 268–272; Scheidel 2007: 332.For large estates created by the first round of proscriptions, see Roselaar 2010: 285–286.
[20] Fortunes of supporters: Shatzman 1975: 400, 437–439; Mratschek-Halfmann 1993: 78, 97,111, 160–161.For the emperors’ assets, see Millar 1977: 133–201.Mratschek-Halfmann 1993: 44 (Augustus).Scale of confiscations: 52–54; Burgers 1993.Hopkins 2002: 208 aptly writes that by seizing and handing out wealth, emperors created “replacement aristocrats.”Total national wealth and elite wealth conjectured from Scheidel and Friesen 2009: 74,76 and Piketty 2014: 116–117 figs.3.1–2, using 1700 France and England as analogs for national wealth as a multiple of annual GDP.
[21] Mratschek-Halfmann 1993: 106–107, 113–114, 214;《拉丁铭文选辑》(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1514。
[22] Mratschek-Halfmann 1993: 53, 58, 138–139; Hopkins 2002: 205.
[23] Scheidel 2015a: 234–242, 250–251.
[24] Mouritsen 2015 provides a succinct summary.See also Jongman 1988, esp.108–112(population), 207– 273 (social inequality).A larg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ighboring city of Herculaneum appears to have consisted of slaves and ex-slaves: De Ligt and Garnsey 2012.
[25] House sizes: see herein, chapter 9, pp.267–269, and, more specifically, Stephan 2013: 82, 86(Britain), 127, 135 (Italy, with conflicting results for two different data sets), 171, 182 (North Africa).骨骼数据仍然需要更细致的分析,以决定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人类身高的不平等程度是否也上升了。For the income sources of senators and knights, see Mratschek-Halfmann 1993: 95–127, 140–206; cf.also Andermahr 1998 for senatorial landownership in Italy.
[26] Scheidel and Friesen 2009: 63–74, 75–84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tate share), 86–87 (Gini and extraction rate), 91 (GDP).Cf.also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 for a Roman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in the high 0.3s and an extraction rate of 75 percent.For other societies, see ibid.and herein, p.100.For economically middling Romans, see Scheidel 2006; Mayer 2012.
[27] Investment and land acquisition: Jongman 2006: 249–250.Olympiodorus: Wickham 2005: 162; Brown 2012: 16–17; Harper 2015a: 56–58, 61 (plateau).如果后来的帝国更为贫穷,报告出来的财富数量实际上在相对意义上是比较大的:尽管这是不能排除的,但很少有证据支持Milanovic 2010: 8 and 2016: 67–68, esp.68 fig.2.9猜测出来的平均人均GDP的剧烈下降这样的说法;cf.herein, p.88.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Roman aristocracy, see herein, chapter 9, pp.264–266。
[28] Egypt: Palme 2015, with Harper 2015a: 51.For earlier land concentration in Roman Egypt,see herein, chapter 11, p.325.Italy: Champlin 1980, with Harper 2015a: 54.More detailed land registers from the fourth-century CE Aegean document smaller holdings of not more than 1,000 acres: Harper 2015a: 52 table 3.6.Super-rich: Wickham 2005: 163–165.
[29] Byzantine inequality: Milanovic 2006.
[30] Borsch 2005: 24–34 for the Mamluk system; Meloy 2004 for the rackets.
[31] Yaycioglu 2012; and see also Ze’evi and Buke 2015 for the banishment, dismissal, and confiscation of the possessions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pashas).
[32] Powelson 1988: 84–85, 220–229; herein, chapter 8, pp.241–242.
[33] Powelson 1988: 234–239.
[34]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172–173; with http://gpih.ucdavis.edu/files/Paris_1380–1870.xls (wages).
[35] 28 societies: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 and herein, Appendix,pp.447–448.Athens in the 330s BCE: using conversions of 1 drachma = 7.37 kg of wheat= $8.67 in 1990 International Dollars, per capita GDP and the income Gini were $1,647 and 0.38 according to Ober 2016: 8, 22; and see 9 for the extraction rate.Cf.Ober 2015a:91–93; 2015b: 502–504 for values of $1,118/0.45 (“pessimistic” scenario) and $1,415/0.4(“optimistic”).Comparanda from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Maddison project.尽管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的数据集对Boix 2015:258–259推测的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国经历了差异化不平等的说法提出疑问,只要我们聚焦到直接民主制和其他政府形式的对比,古代雅典的例子就可能会为其模型提供一些支撑。
长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权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与非洲类人猿一起在几百万年前就出现了,并且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减弱了。全新世期间,人类驯化活动推动了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一次上扬,并随着我们描述过的大规模的掠夺成性的国家形成而达到顶峰。现在是时候对这个地球的特定部分进行放大,以看清楚其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化是否更加普遍地遵循一种能够被特定的不平等和矫正力量解释的模式。我的目标是证实这本书的关键论点: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
我会把大家一路带到20世纪早期的调查中,我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聚焦欧洲的,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欧洲社会产生了最丰富的(或者至少是最彻底研究过的)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关于物质不平等演化的证据。这一证据使得粗略重现几千年来上升或稳定的不平等和平等化冲击之间的反复变动有了可能性(图3.1)。
公元前7000年起,欧洲出现了农业,并且农业在接下来的3000年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宽泛地说,哪怕我们不能期望可以细致地追踪这一过程,这一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注定要伴随着逐渐升高的不平等。设想一个直截了当的线性轨迹是不够明智的,例如瓦尔纳那些考古证据表明,短期的变动也可能是相对可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退后一步,而是退后三步或者更多,把我们的考察尺度从几百年扩展到几千年,我们也许可以安稳地设想一种人口密度增加、规制强化和剩余增长的总体向上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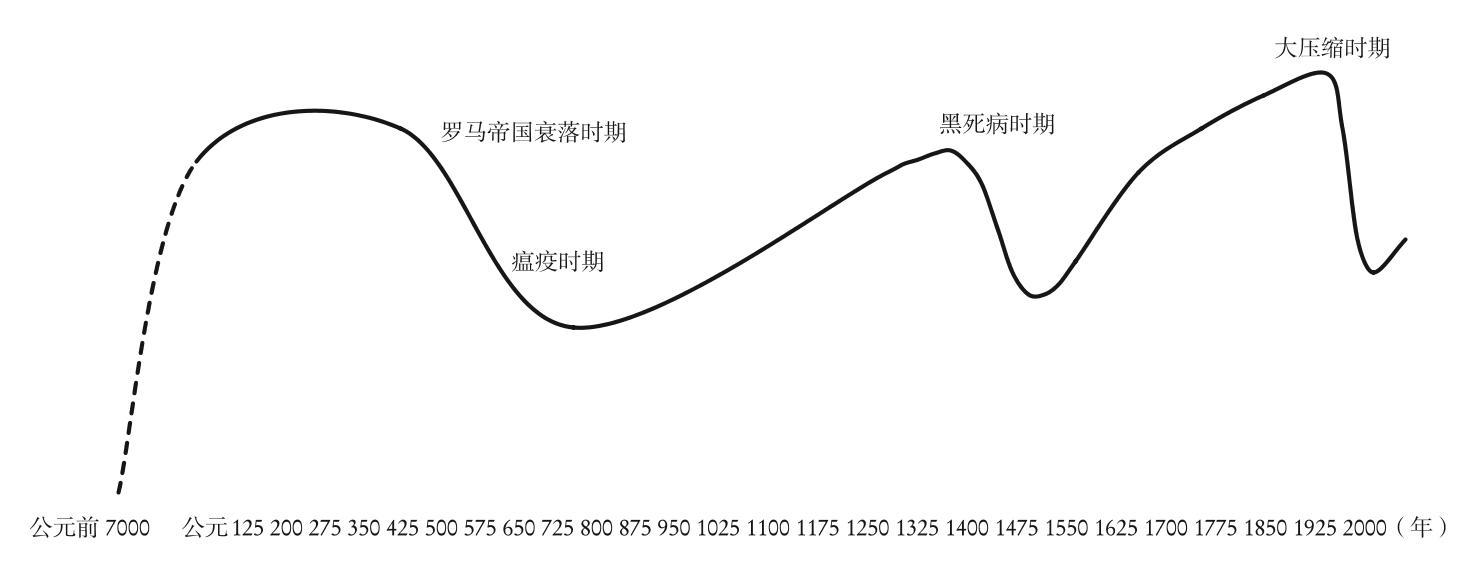
图3.1 欧洲长期的不平等趋势
基于这种俯瞰的角度,我们能够确定,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成熟期中,物质不平等达到第一个长期最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前没有达到过与之相当的人口、城市化、私有财富和强制能力的水平。希腊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它与古代西亚文明核心区域地理上的邻近性,其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地区在时间上往前回溯更远。高水平的不平等在迈锡尼铜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达到,并且也许在公元前13世纪达到顶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随着宫殿变成村庄,国家的崩溃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这就是我在第9章中讨论的暴力解决措施。尽管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文化(大约公元前800—前300年)取得了高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比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高),根植于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制度限制了不平等。然而,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罗马时期也同样是一个区域不平等大大上升的时代。 [1]
暂且不谈巴尔干地区的南部,这里依然是在拜占庭的控制之下(有时是不稳定的),所有受到罗马统治的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严重压缩,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5世纪的下半叶,即罗马政权分裂的时候。就像我在第9章中表明的,这种经济平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衰败的结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暴力性冲击,并且被从6—8世纪在西欧发生的,提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价值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当大变化:矫正效应可能在后罗马帝国时期的英国最为彻底,早期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大体上都被一扫而空,不平等可能在更封闭的地区表现得更有弹性,例如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这样,广泛的精英利益交换网络、城市化、财政结构和跨区域财富持有的瓦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 [2]
试图对这次大压缩进行量化似乎是不明智的:为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很困难,为6—8世纪的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可能是更困难的。注意到以下两个下行压力的同时发生就足够了:降低了不平等范围的人均剩余的缩小,以及国家和精英的榨取能力的逐渐变小。即使是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也受到了可以缓解暴力性动乱的严重影响。有一段时间,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城市化的最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可能是帝国的不平等的最后残存的堡垒,但即使这个受到很好保护的中心也经历了一段严重衰退的时期。 [3]
欧洲经济和国家组织开始在不同时期复苏。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的扩张可以被视为一段不平等复活的时期,也许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也如此。在英国,在埃赛克斯伯爵的领导和强大且富有的贵族形成的条件下,后罗马时代的低谷让位给国家的形成。拜占庭这样一个权贵主导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重新掌握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普遍变得衰弱的贵族重新开始聚集力量。考虑到相当大的地理差异,9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日益突出使得精英阶层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农业劳动力及其剩余,这是一个与民间和宗教领袖之间正在进行的土地集中同时发生的过程。大约1000—1300年以来,欧洲随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阶段。更多人口、更多更大的城市、更多商业和更优良的精英阶层,所有这些都提高了经济不平等程度。
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虽然1086年的《土地赋税调查书》表明,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从他们自己的地块就可以获得超过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但1279—1280年的《百户区卷档》发现,他们后代中的大多数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收割工作获得工资收入,补充他们的农业生产,使得自己收支相抵。模拟模型显示,单凭人口增长不足以产生这一结果:不平等的上升是由人口数量上升的交互效应驱动的;这种土地转移政策的放松鼓励了小土地所有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把土地卖给状况好一些的人,以购买食品、种子、牲畜,或者偿还债务;可分割遗产带来的效应是打破了财产的持有规则,并且促进了更多的压力环境下的出售。一些农民变得完全没有任何土地,这更进一步提高了资产不平等。此外,即便这些人的地产规模在缩小,英国的地租在11—14世纪早期之间却大大增加了。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即9—14世纪早期之间,典型的地块大小从大约10公顷下降到常常少于3公顷。 [4]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程度也受到了上层社会收入和财富集中的驱动。1200年的英格兰,有160位富豪(男爵)的平均收入达到200镑,但是到1300年,这一群体已经扩大到200人,平均收入为680镑,扣除物价因素也有原来的两倍。作为一个不平等程度强化的典型时期,最大的财富增长得最多:在1200年,最富有的男爵,切斯特的罗杰德莱西用掉了800镑(也许是所有同级别群体平均年收入的4倍),然而到1300年,康沃尔伯爵埃德蒙得到3800镑,扣除物价因素后几乎有其三倍之多,等价于这时期所有同级别群体人均收入的5.5倍。英国精英阶层的中间等级增长得更为显著,束带骑士的数量在大体相等的收入门槛上,从1200年的大约1000人上升到1300年的3000人。军队报酬的不平等能够通过骑士阶层相对于步兵的收入比率来追踪,这一数字从1165年的8∶1上升到1215年的12∶1,再到1300年的12∶1~24∶1。并非巧合的是,在14世纪的早期,法国葡萄酒的进口也达到顶峰。同一时间,精英的收入在实际水平上也上升了,那些普通人的收入则下降了。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的交互效应很可能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 [5]
在1347年暴发黑死病的前夜,欧洲整体上要比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更为发达和更不平等。我们只能猜测这两个顶峰的对比。我怀疑甚至到14世纪早期,整体的不平等可能已经下降到比大约1000年之前的水平低一些。在中世纪欧洲,没有能和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相媲美的人物了,他们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及其腹地拥有资产,并从庞大的帝国财政中汲取资源。只有拜占庭帝国可能遭遇过比成熟的罗马帝国更高的榨取率,但是它主要位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之外。一项对1290年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孤立估计,其不平等程度用人均产出的可比水平表示,要比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水平稍微低一些。最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中叶之前对不平等的更有意义的对比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在这里,重要的是中世纪中叶收入和财富的整体不平等,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的趋势。14世纪第一个10年巴黎和伦敦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达到0.79或者可能更高)的税收记录仅仅记载了那段时间的长期性商业革命靠近终点的情况。 [6]
当瘟疫在1347年袭击欧洲和中东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几代人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瘟疫蔓延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到1400年,超过1/4的欧洲人口被认为已经死去——也许在意大利是1/3,在英格兰是接近一半。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到15世纪中叶,在这个区域,非熟练的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提高了一倍,但是熟练的手工艺人提高得少一些。即使地租下降和精英阶层财富缩减,英国的农业工资的实际值也翻番了。从英格兰到埃及的平民享受到更好的食物,并且身体长得更高了。如同我在第10章所指出的,意大利城市的税收记录展现出财富不平等的戏剧性下降,本地或者区域的基尼系数下降了超过10个点,上层社会的财富比重下降了1/3或者更多。几百年的不平等化过程被人类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冲击化解了。 [7]
瘟疫在15世纪末消退之后,欧洲的人口开始复苏。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不平等也是如此。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海外殖民帝国的创立,以及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扩张促进了制度变迁和新的交易网络产生。尽管商业性和朝贡性的交易一直都是并存着的,但随着附庸国的商业化转变以及对商业收益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前一种交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更为统一的世界系统的增长得到新世界中金银的开采和跨大陆贸易调动的财富支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当欧洲变成世界性交易网络中心的时候,发展带给商业精英更多的力量,并且把农村大多数人拉进了对他们的土地依附带来压力的市场活动之中。获得进贡的精英阶层演变成商业和企业化的地主,同时商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圈地、税收、债务和持有土地的商业化,农民被逐渐从土地中剥离了。根植于对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应用的传统致富方式与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一起持续存在:更强大的国家提供了通向富裕的有吸引力的路径。所有这些都对财富不平等施加了上行压力。 [8]
中世纪后期,现代欧洲在物质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财富分配(然而还不是收入)的量化证据首次变得可用了,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追踪长时间的变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发展的成果。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可征税财产的本地记录,并且得到了有关地主和工人收入信息的补充。接下来,我将同时使用财富分配和收入的信息。一般来说,系统分析这一时期的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研究前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比现代经济学家选择的更折中。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前工业化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基本不太可能向不同方向移动。 [9]
尽管这些数据集并不意味着关于不平等的真实全国统计数据,但它们把我们对于财富集中的结构和演化的理解置于一个比以前更坚实的基础上。由于它们的内在凝聚力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一些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数据可能对这些变化的总体轮廓来说是更为可靠的向导(相对于从不同来源的,即使是19世纪的资料来重构全国趋势的现代尝试而言)。几个西欧和南欧社会得到的证据表明,资源在大城市中要比在较小的城镇或者乡村中分布得更不均衡,不平等程度在黑死病结束之后通常都上升了,这种上升发生在多种经济条件的作用之下。
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技能和收入的差异化,精英家庭和商业资本的空间集中,以及更贫穷的移民的流入总是推高了城市的不平等程度。根据1427年的佛罗伦萨王国人口统计,财富不平等与城市化的规模是正相关的。都城佛罗伦萨有着一个达到0.79的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如果把没有记载的无财产穷人包括在内,也许接近0.85。较小城市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0.71~0.75),农业平原的还要低一些(0.63),最贫穷的地区(丘陵和山区)的最低(0.52~0.53)。最高等级人群的收入相应发生类似的变化,从佛罗伦萨最高5%收入人群所占的67%的比重,下降到山区同类人的36%的比重。另一个意大利税收登记数据中出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15—18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这些城市报告的财富集中程度一直比相邻的农村地区高一些。在皮德蒙特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模式,虽然程度轻一些。 [10]
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西欧早期的主要城市中,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5的较高财富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标准特征。奥格斯堡是当时德国领先的经济中心之一,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从与瘟疫相关的矫正作用下复苏之后,城市财富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超常规的0.89。很难想象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区:很少比例的居民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资产,另外1/3~2/3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会在第11章详细讨论这一案例。在荷兰,大城市同样有着类似的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在0.8~0.9之间),小城镇则落在后面(0.5~0.65)。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其相应的基尼系数在1742年达到0.69。1524—1525年的英国税收记录反映出的城市财富基尼系数通常都高于0.6,也可能高达0.82~0.85,要比农村的0.54~0.62高出不少。在个人财产的遗嘱清单里,资产的分布同样与住房的规模相关。1500—1800年之间,在这些区域的某些地方,城市化比率保持了稳定,最为显著的是在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在英格兰和荷兰,城市化比率有了显著的增长,由此提高了整体不平等水平。 [11]
从15世纪时由黑死病带来的矫正效应的低点开始,在我们有数据的几乎欧洲所有地区,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荷兰在这方面提供了最详细的信息。作为一个早熟的,几乎确定有着当时全世界最高人均GDP的发达经济体,它证明了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效应。在17世纪晚期,城市人口比例达到40%,同时只有1/3的人口从事农业。大城市为出口市场进行制造和加工。脆弱的贵族阶级已经被享有免受专制掠夺的自由商业精英超越。由于资本集中在城市,以及许多地主居住在城市,城市变得高度不平等了。在1742年的阿姆斯特丹,几乎所有收入的2/3来自资本投资和创业活动。作为对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的转移和压低了实际工资的国外劳动力流入的反应,荷兰的资本收入的比例从1500年的44%上升到1650年的59%。 [12]
荷兰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即使在城市贫民队伍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新创造财富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份额,经济发展和城市增长带来的是长期上升的不平等程度。在莱顿市已报告财富的最长可得时间序列中,顶层1%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从1498年的21%上升到1623年的33%、1675年的42%和1722年的59%。在同一时期,资产总额没有达到最低税收门槛标准的家庭比例从76%上升到92%。相关度最高的信息来自记录了荷兰不同区域房屋年度租金值的税收登记表,这是总资产不平等水平的一个更为间接和不完美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富人如果变得更富有,他们在住房上花费的收入比例会逐渐变小,这就可能会带来对不平等水平的低估。荷兰大部分地方的加权值显示出一种持续的上升,从1514年的0.5到1561年的0.56,18世纪40年代的0.61或者0.63,以及1801年的0.63。在1561—1732年间,租金的基尼系数在所有地方都上升了,在城市中从0.52上升到0.59,在乡村中从0.35升到0.38。对15个荷兰城镇资料的最新标准化调查显示出一个从16世纪—19世纪后期总体上升的趋势。 [13]
经济进步仅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有时即使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财富集中还保持上升。只有在北方低地国家中,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而在南方低地国家中,这两个变量之间根本没有系统性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影响不平等上升的共同趋势。不同的税收体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南方对累退的消费税的强烈重视本应该产生不平等的后果,然而荷兰共和国对北方的税收实际上是累进的,关注的重点是奢侈品和不动产。可是,不平等还是在整个区域逐渐扩大。
这并不奇怪:在更有活力的北方,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成为全球贸易和城市化的不平等力量的一部分,它至少部分根植于社会政治的权力关系。在1580—1789年间的阿姆斯特丹,高级行政官员、教士、校长以及兼任医生的理发师的工资上升得更快——以5~10的倍数,相对于木匠获得的工资而言,后者仅仅翻了一番。对于一些职业,例如外科医生,这可能反映了赋予他们的技能更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时期工人的技能溢价并没有普遍上升。此外,对政府官员和例如校长这样相关的“知识性工人”慷慨加薪,很可能最初是由一种人的欲望驱动的,这种人紧跟这些人,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并且从增长的资本收入中获益。因此,商业资本的收入对特定的社会特权群体而言,可能对工资有一种明显的冲击效应。精英阶层的寻租行为对于收入分配有一种极化效应。 [14]
在佛罗伦萨境内,财产登记记载表明,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5世纪中叶0.5的低点增长到1700年左右的0.74。在阿雷佐市,它从1390年的0.48上升到1792年的0.83,在普拉托从0.58(1546年)增长到0.83(1763年)。这一集中趋势最主要是由最高层人群的财富比重增长驱动的:在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之间,佛罗伦萨境内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已知资产的比重从6.8%上升到17.5%,在阿雷佐是从8.9%变成26.4%,普拉托则是从8.1%上升为23.3%。从皮德蒙特地区的各种登记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在一些城市,财富的基尼系数的增加可以达到27个点,一些农村社区也达到相似的规模。在那不勒斯王国的阿普利亚区,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比例从1600年前后的48%增长到1750年的61%。在皮埃蒙特和佛罗伦萨,财富最少达到本地中位数值10倍的家庭比例从15世纪后期的3%~5%上升到10%~14%(三个世纪后):随着更多家庭脱离中位数水平,两极分化加剧了。 [15]
荷兰的情况与其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大多发生在17世纪经济停滞甚至更长期的缺乏城市化进展的环境当中。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从黑死病的消耗中恢复的人口;对农业生产者的逐步征用和无产阶级化;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压低了其相对于土地和其他资本的价值。精英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在荷兰和法国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此外,具有自治社区的传统,以及公民与共和主义强大观念的城邦被纳入征收更重税收的更大和更多强制的国家。在皮德蒙特和南部低地国家,公共债务把资源从工人引导到了富有的债权人那里。 [16]
这些案例研究强调了不平等机制的长期持续性。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巴比伦时期,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提高了不平等水平。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同样也是如此。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富裕的资本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通过财政攫取维持的精英阶层的富裕,以及其他政府活动有着更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苏美尔人时期。现代社会早期的收入和财富集中仅仅在方式和规模上有所差异:与更传统的寻租策略一起,精英阶层现在可能从购买公债中获益,而不是直接窃取或者勒索资源,全球贸易网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城市化水平空前。然而在本质上,不平等的主要方式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在由暴力性冲击导致的一次短暂中断之后,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
这些行之有效、公认的不平等因子的有效补充,对解释大范围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得到的相似结果大有裨益(图3.2)。在荷兰共和国,由于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不平等程度得以提高,然而财政压力看起来是皮德蒙特和托斯卡纳的农村无产阶级化的最关键因素,它们在南方低地国家都发挥着作用。在英格兰,即这一时期北方低地国家之外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商业化和城市扩张提高了财富差距:诺丁汉的财富基尼系数从1473年的0.64上升到1524年的0.78,同时在一个个人财产遗嘱清单的调查中,基尼系数从16世纪上半叶的0.48~0.52(在接下来的80年里)上升到0.53~0.66。在这些记录的9个样本中,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占所有资产的13%~25%,后来则占到24%~35%。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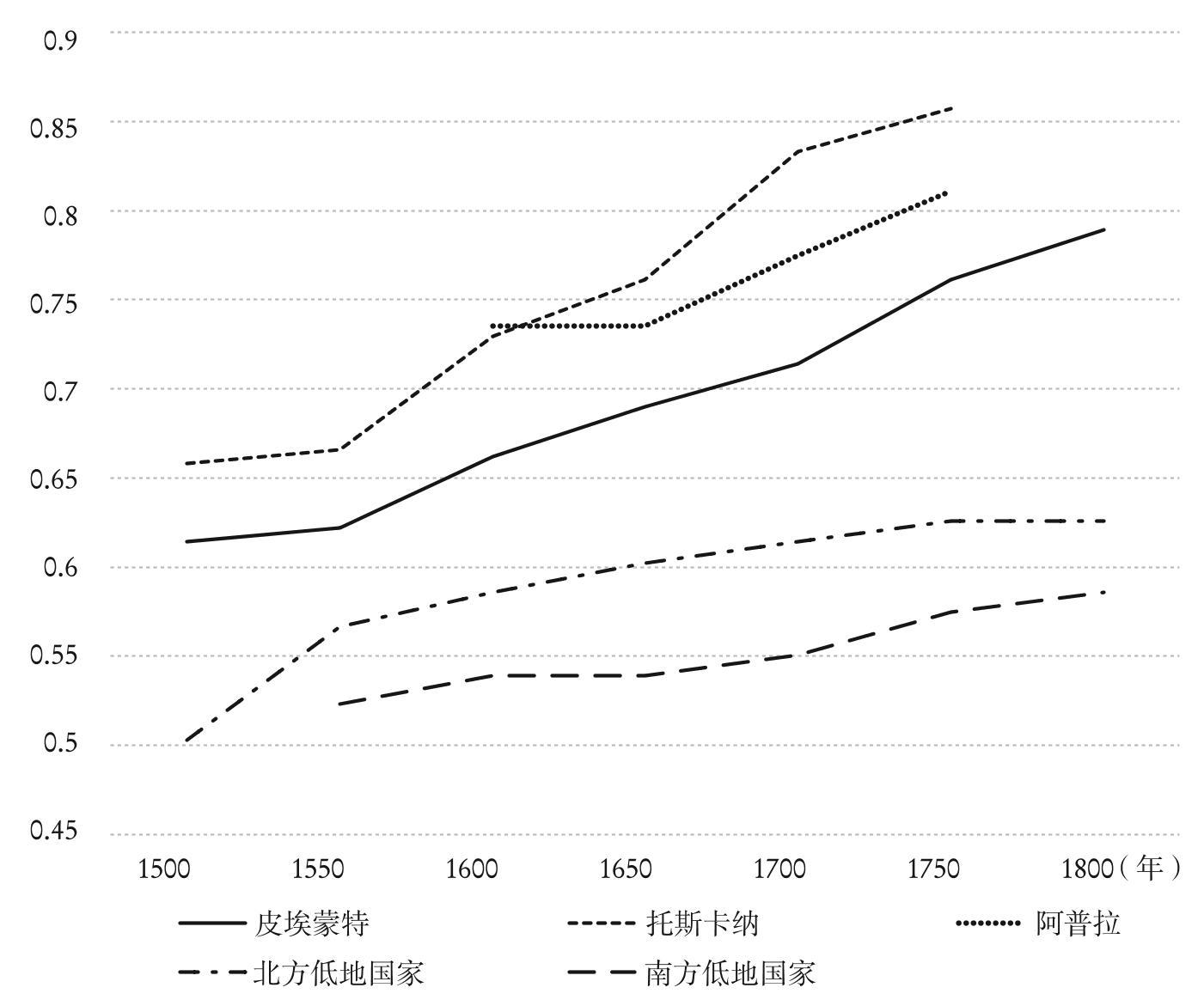
图3.2 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1500—1800年
西班牙的经济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它经历了乡村化——从畜牧业到农业的转型,以及低工资。在经济停滞甚至紧缩的背景下,名义人均GDP与名义工资之比从15世纪20年代—18世纪末一直在稳定上升,反映出伴随着实际工资下降的一种持续进行的不平等的劳动力贬值,这也是我们在很多欧洲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另一种不平等指标,即地租与工资之比,在这一时期有更大的波动,同样,1800年的要比400年前的高得多(图3.3)。这些发现与在马德里省得到的观察十分相符,从税收记录中重建的财富不平等在1500—1840年间上升了,不过是以一种非连续的方式进行的。 [18]
在16世纪初的法国乡村,人口复苏和不断增长的庄园的双重压力,使得介于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和由于农场太小而不能养活自己的小佃农之间的中等大小的本地社群空心化了,迫使后者变成了雇佣劳动力。目前,葡萄牙是唯一一个已知的例外。根据税务记录,大约在1565—1700年间,在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陷入停滞,以及被海外帝国的殖民弱化的环境中,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技能溢价大体上维持稳定,而地租与工资之间的比率在18世纪70年代获得部分恢复之前,在整个17世纪都在下降。更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收入不平等的温和下降大多发生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城市的不平等在长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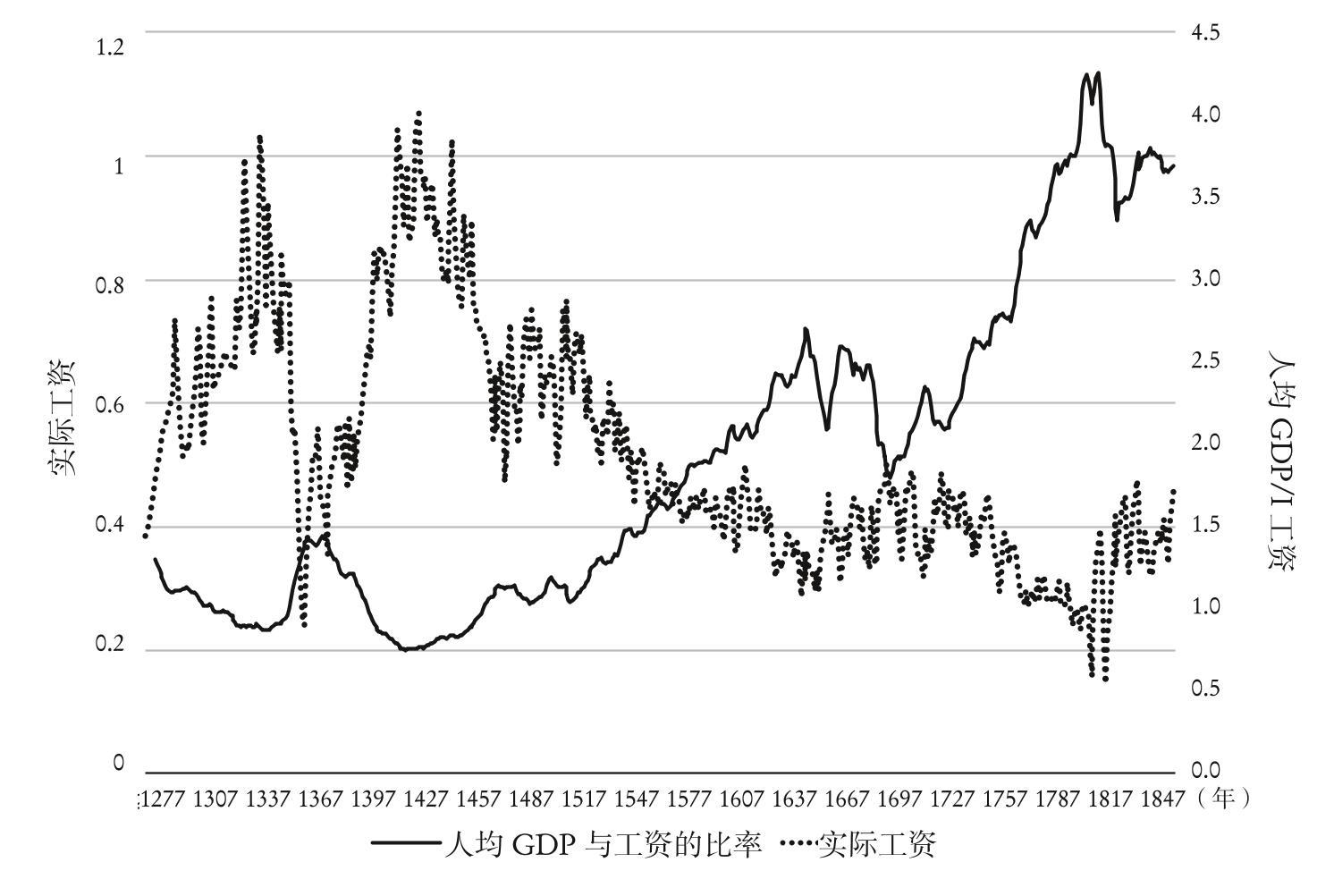
图3.3 西班牙人均GDP与工资以及实际工资的比率,1277—1850年
如果没有暴力压制,不平等水平可能因为本地经济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各种因素而上升,但它(几乎)一直上升。无论好坏,为这一时期设计出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现代尝试,大体上与更为本地化的经验数据集合所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荷兰的整体收入不平等,在1808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回落到0.57之前,已经从1561年的0.56上升到1732年的0.61。考虑到基本原理计算的不稳定基础,这些数字应被视为相当高的和稳定的不平等水平的一种象征。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应的基尼系数从1688年的0.45(比0.37的公认中世纪峰值高出不少)上升到1739年的0.46和1801年的0.52。在1788年的法国,基尼系数同样高达大约0.56。所有这些数值都要比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数值要高,人均产出也是如此:大体上是荷兰最低生活标准的4~6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7倍,法国的4倍,大约相当于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英格兰基本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然而,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并不是通向更高不平等的唯一路径:在维持最低生活收入的2.5倍的水平上,1752年的旧卡斯蒂利亚并没有值得夸耀的、比古罗马多得多的人均剩余,但有着很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0.53),这反映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化力量的影响。 [20]
在所有能够大体估计出这些数值的例子中,有效榨取率(给定人均GDP水平上最大可行不平等的实现比例)在16—19世纪初期或者保持水平,或者上升。黑死病减弱之后的3个世纪,在西欧和南欧那些有着更好资料的地方,收入不平等已经在名义上(以总基尼系数表示)第一次达到超越之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用对人均GDP比较敏感的有效生存需求进行调整之后,它们大体上与那些生活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中叶的人群接近。毫无例外,1800年的城市工人实际工资要比在15世纪后期的水平低一些,同时,尽管经过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化生活成本指标调整的“真实”不平等水平要比名义上的测度波动性更大,总体趋势同样是向上的。 [21]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来自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4个城市的遗嘱清单记录了全部的资产,包括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例如现金、贷款和借款,揭示了1500—1840年间财富不平等的演进。在欧洲,平均财富和不平等水平与城市的规模是呈正相关的。在三个有全面数据的城市中,资产集中的基尼系数在1820年和1840年要比这些序列开始的时候更高,从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一直在变动。这同样基本适用于最高收入者的财富份额。农村遗嘱清单的总基尼系数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的0.54上升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0.66,这是一个可能与农业的商业化,以及以不断下降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不断扩张的私有化为特征的,与不断变化的产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增长。财富不平等中所能观察到的增长也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证据是一致的。因此,爱琴海东部地区的不平等趋势与西欧和南欧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 [22]
在继续讨论从“漫长的19世纪”一直到“一战”的这段时间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在全球其他地区,与图1.1类似的对几千年不平等轮廓的重构是否可行。目前,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猜测,但不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证明,即中国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波动与所谓的它的“王朝更迭”形成映射。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中试图展现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汉朝的长期统治之下,不平等程度上升了,而且它可能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的东汉后期达到顶点,就像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完整统一帝国的最后阶段达到巅峰一样。从4世纪早期—6世纪后期,延长的“分裂期”很可能见证了一定程度的压缩,特别是在这一区域北部,大量短暂的外国征服者政权和后来经历了大规模动员战争、雄心勃勃的土地分配、计划复兴的王朝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争夺。 [23]
如同第9章所描述的,在6—9世纪的唐朝统治之下,一直到其精英阶层解体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被消灭之前,收入和财富注定都获得了增长且变得更为集中了。宋朝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可能产生了与现代欧洲早期一些地方所观察到的类似的不平等结果,在后来的南宋时期,大地主是强大的。随着经济衰落、瘟疫、入侵和掠夺性统治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元朝时期的趋势更难确定。在明朝统治下,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了,尽管用国际标准来看是有益的,其总水平在清朝末期之前并不是特别高。除了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和200年后在英国控制下的高度不平等进一步证实了大规模掠夺性帝国或者殖民统治的不平等效应之外,这里关于南亚可以说的就更少了。 [24]
对于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新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只能以一种高度写意的方式进行简述。15世纪时,随着进贡的流动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强大的精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世袭资产,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形成很可能将经济差距扩大到新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期间,抗衡性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少数征服者精英完成的西班牙扩张和掠夺性殖民统治可能维持,甚或提高了现有的财富集中水平。我在第11章描述的新的“旧世界”传染病的到来导致的灾难性人口损耗,使得劳动力变得稀缺,甚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推高了实际工资。即便如此,在这些传染病消退之后,人口得以恢复,土地和劳动力比率下降,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统治得到了全面巩固;到18世纪,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水平也许和从前一样高了。19世纪初的革命和独立可能产生了平等化效应,直到该世纪下半叶的商品繁荣把不平等推向了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只有间歇停顿的收入集中过程(图3.4)。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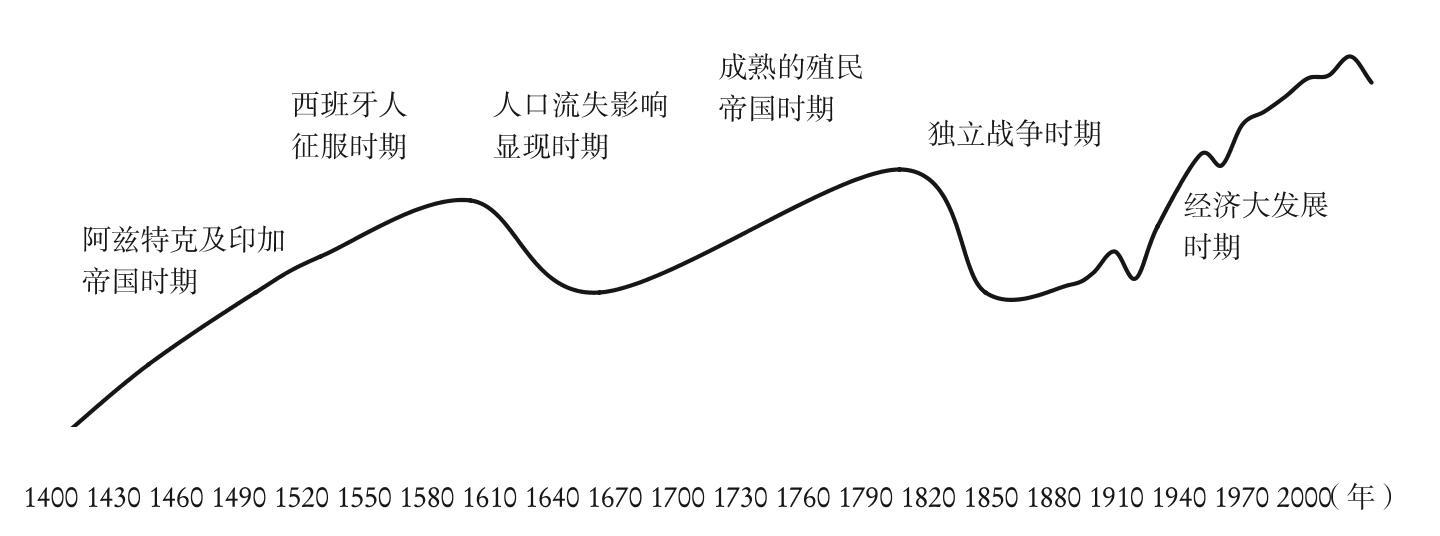
图3.4 拉丁美洲长期的不平等趋势
这把我们带到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从当地数据集到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估计的一致性转换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仅仅是这个原因,工业化是否令英国不平等的问题恶化就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难以应对的了。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1700年—20世纪早期,私人财富集中得到了稳定的强化,在此期间,实际人均GDP变成了之前的三倍多。因此,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00年的39%上升到20世纪早期的69%。到1873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系数已经上升到0.94,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平等不可能进一步增长了。关于收入分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晰。来自纳税申报表和各种社会信息表格,以及地租与工资比率的证据相当明确地指出,收入不平等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初出现了增长。此外,尽管从房产税数据和报告的工资得到的住房不平等的信息已经表明,在19世纪的上半叶,收入在继续变得更为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特殊资料能够承受多少压力依然是存在争议的。 [26]
关于不平等的各种指标在19世纪上半叶或者前2/3的时间里上升,随后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都在下降的较早观念更为准确,从而产生了一个平缓的倒U形曲线,这就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转型社会中,经济现代化首先提升然后降低不平等水平。工资分散度在1815—1851年间上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接着一直下降到1911年的观察结果,可能是不同行业的基础数据的假象,显示出相互矛盾的趋势。类似地,从房产税数据中构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的测度指出,对有人居住的房子,基尼系数在1830年和1871年分别是0.61和0.67,对于私人住宅,则从1874年的0.63下降到1911年的0.55,我们不能轻易地仅凭表面就信以为真。收入份额的清单也没有太大用处。修订后的社会统计表格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相当稳定的程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01及1803年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2,1867年是0.48,整个英国在1913年是0.48。精确性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在19世纪,英格兰或者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大体保持不变。 [27]
意大利的结果也同样不能确定。近来关于意大利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指标,都指出了1871年至“一战”(及以后)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基本稳定性,这与较早的关于家庭总预算的调查结果形成对比,后者显示1881年和战争期间不平等水平逐渐下降,这是一个由工业化导致的不平等效应被向西半球的大规模移民抵消的时期。国民收入数据对法国来说是不可得的。在巴黎,以顶层1%群体的资产在其个人财富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的财富集中度,从1807—1867年间的50%~55%上升到1913年的72%,这个比例在顶层0.1%群体中上升得更为猛烈,从15%~23%上升到43%。在整个国家,精英的财富比例更为稳定地从1807年的43%(顶层1%群体)和16%(顶层0.1%群体)分别增长到1913年的55%和26%。西班牙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到“一战”期间一直上升。 [28]
这一时期的德国的数据也不存在。在普鲁士,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874年的13%或者15%上升到1891年的17%或18%。在1891—1913年之间的净趋势是平稳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年当中大体上保持不变,它们以一种顺周期的形式变动,与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最详细的普鲁士收入基尼系数调查追踪到了从1822年一直上升到1906年的顶峰的一条路径,然后一直到1912年出现一个小幅下降,再到1914年出现部分恢复。由于“一战”的爆发在那个时点截断了不平等的“和平”演化,我们无法分辨这一简短的下降仅仅是暂时的中断,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转折点。在荷兰,19世纪是经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的一段巩固期。不平等还没有完全走完其发展历程:在1808—1875年间,在10个省中,可租赁房屋价值分布的基尼系数8个有所上升,高收入群体中的不平等增长从1742年延续到1880年,再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然而,在同一时间,实际工资回升,技能溢价下降。国民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似乎在1800年和1914年是相似的,这就意味着不平等大体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了。 [29]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供了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但有时令人费解的信息。1870年在丹麦的一次评估估计顶层1%收入群体中的已婚夫妇和单身成人的收入份额为19.4%。这些报告在1903年被重新恢复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16.2%,到1908年达到16.5%,伴随着也能在其他中立国家中观察到的由“一战”中的牟取暴利诱发的短暂的暴力潮。尽管1870—1903年间隐含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并不是剧烈的,但我们必须怀疑早期资料的可靠性。 [30]
类似的保留意见适用于有关1789年发生的一次性税收的记录,这一记录被用来表明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0.7,这一数值意味着不平等程度接近,甚至等于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担忧使人们很难想象,18世纪末—20世纪初收入不平等在持续衰减。相比之下,关于18世纪末大地主的统治性地位的报道,为那些指出从1789—1908年,在丹麦社会中最富有的10%群体中存在显著的财富分散的计算提供了可信度。 [31]
挪威和瑞典的发展同样提出了关于记录质量的问题。在挪威,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重,从计算得到的1789年的较高水平处下降,在1868—1930年之间稳定维持在36%~38%。1875—1906年,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在18%~21%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变动得非常少,但是到1910—1913年,突然下落到大约11%。这很难解释,1908年和1909年的衰退是否足以说明这一分化还不清楚。如果这种下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证据的假象,它就表明存在某种冲击驱动的矫正事件。瑞典的趋势与挪威的类似,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03年的27%下降到1907—1912年的20%~21%。然而,1870—1914年,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同时与丹麦和挪威不同,财富集中程度在1800—1910年间略微增加了。 [32]
在后来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地区,不平等可能持续增长了250年的时间,仅有一些很短暂的停顿(图3.5)。殖民地时期的趋势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即使是这样,可能奴隶制的扩张还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提高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伴随着战争毁灭了资本、军事服务,伤亡、逃跑的奴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海外贸易受到破坏,以及城市精英不成比例地受到这些混乱局面的沉重打击,独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给不平等)带来了暂时性的压制效果。富裕的效忠者逝去了,其他人最后一贫如洗,同时,城乡工资,白领与非技能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800—1860年,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工业和城市的技术进步以及金融机构的改善,使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1860年底,全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和1850年的0.49上升到0.51,同时这“1%”,从1774年的8.5%和1850年的9.2%增加到获得10%的总收入,蓄奴州通常记载了更高的不平等水平。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财产集中的急剧增长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大规模上升都有助于这一发展: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74年的14%变成了1860年的32%,是原来的两倍多,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9暴涨到0.47。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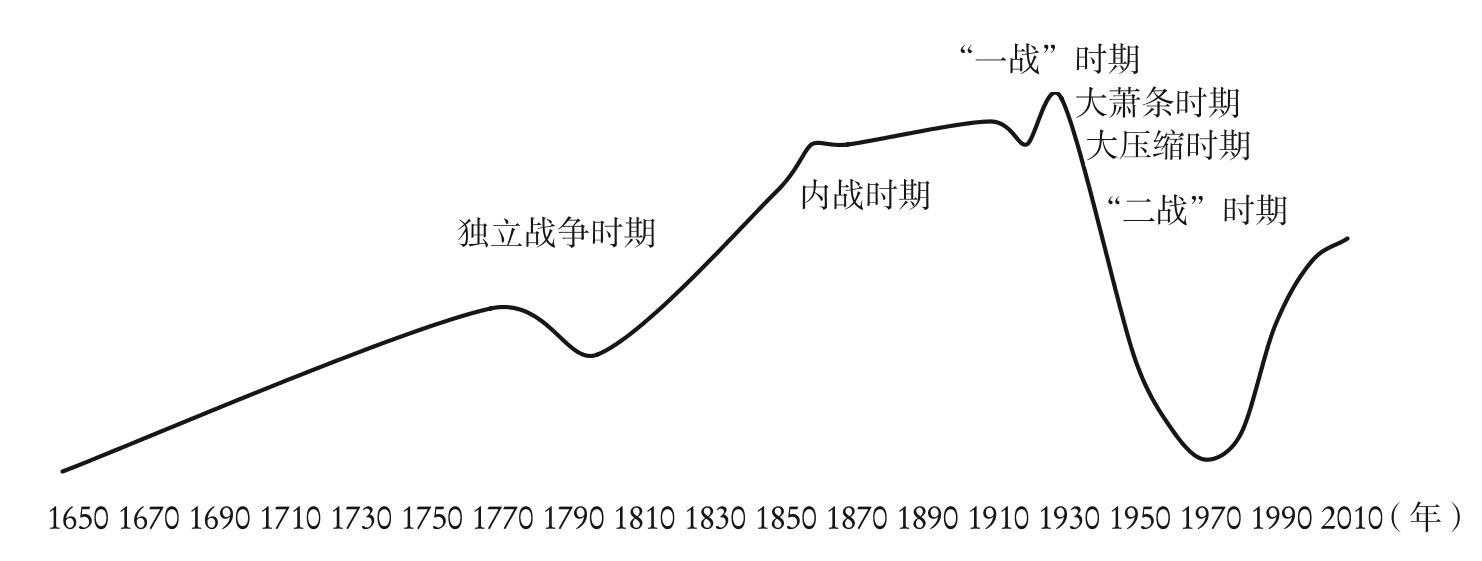
图3.5 美国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
我在第6章中会更为详细地描述,内战使得南方的财富趋于平衡,但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这两种相互抵消的区域性趋势使得国家层面的测度大体不变。不平等随后延续到20世纪初: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从1870年的大约10%变成了1913年的大约18%,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技能溢价也上升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低技能工人的大规模移民是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的一整套指标同样表明了从1640年到1890年,甚至再到1930年的持续性上升。以一种测度为例,1810—1910年间,顶层的1%美国家庭持有的所有资产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上升到46%。财富集中在最顶层是最明显的:在1790年,美国所公开的最大的财富已经等于平均年度工人工资的25000倍,在1912年,约翰·洛克菲勒身价为这一等价工资的260万倍,相当于增加了两个数量级。 [34]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长期性增长。当商品出口使区域精英富裕时,收入集中程度飙升了:对南锥体各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一项估计认为,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575增长到1920年的0.653,另一项分析得出更强烈的上升趋势,即使经过了人口加权,还是从1870年的0.296变成了1929年的0.475。尽管这些数据很不确定,这一趋势的总体方向似乎是足够清晰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技能溢价好像下降了,当日本与世隔绝的情形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时,不平等水平是相当低的。商业精英以前不能通过国际贸易来确保其收益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此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部门在闭关锁国期间的扩张,税收是基于产出的固定假设来设定的事实阻止了拥有大片土地的“300位世袭贵族”获取不断扩大的农业剩余,这就导致他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下降。日本对全球经济的开放以及随后的工业化推动不平等达到更高的水平。 [35]
总而言之,对一个以当前标准来看产生了常常是有限质量和一致性的只有相对较少数据量的时期来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世纪的国家发展趋势就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清晰。对于一段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时期,时间范围取决于各国的可得证据,可以从几十年到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程度主要是上升或者维持不变的。尽管财富的集中实际上大量增加到此前没有的高度,但是在英格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早期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不能再高。虽然在另一个发展较早的不平等国家荷兰(也许还有意大利)较为稳定,然而财富或者收入的差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已经得到充分描述的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日本都上升了。基于对记录的保守解读,除了19世纪富裕人群中一定程度的财富集中和一些突然发生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比例下降之外,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不平等水平。18世纪末、19世纪初至“一战”期间,在我们掌握数据的8个国家中,6个国家的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例上升了: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
同时,对不平等收缩情况的较好记录是罕见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革命带来了温和平等化冲击之后,美国内战是唯一已知的对一个区域的财富集中产生影响的事件。除了这种具有不变的暴力性矫正效应的零星现象外,不平等大多或者维持在高水平,或者进一步扩大了。大体而言,不管这些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还是较晚,甚至完全没有,也不管土地稀缺还是丰富,以及政治系统如何配置,这都是正确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商品和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寻常的和平条件,创造出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并使资本投资者受益的环境。在欧洲,这使得开始于中世纪末期黑死病消除后的长期不平等向上摆动,并且持续了4个多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已经经历了不那么长的不平等化阶段,但是正在进行稳步地追赶。 [36]
在第14章的结尾,我得出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将进入一个收入和财富更为极端分配的不均衡时代的可能答案。但是,这当然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在1914年6月28日上午11点前不久,一个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开枪打死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当时他们乘坐的敞篷轿车正行驶在萨拉热窝街头。当问到他受的伤有多严重的时候,垂死的王储越来越微弱地回应“这没有什么”。他完全搞错了。
36年后,1亿多人死于暴力,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多次遭到破坏。在1914—1945年(或者记录中的最近一年)间,这“1%”的收入份额在日本收缩了2/3;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许还有英国,收缩了超过一半;在芬兰是一半;在德国、荷兰和美国超过了1/3。不平等也在俄国和其原帝国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中国大陆、韩国等地崩溃了。精英阶层手中的财富集中,尽管在革命的环境之外更富有弹性且因此减弱得更慢,还是遵循了同一模式。在西欧,资本存量与年度GDP的比率在1910—1950年间下坠了大约2/3,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接近1/2,这是一个极大降低了富有投资者的经济优势的再平衡过程。暴力性矫正的四个骑士中的两个——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已经释放出毁灭性的后果。这是自黑死病以来第一次,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以来也许无可匹敌的规模上,获得物质资源机会的分配更加平等了,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这次“大收缩”结束的时候(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下跌到自几千年前人类过渡到定居生活和食物驯化以来没有过的深度。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告知其缘由。 [37]
[1] For Varna, see herein, pp.40–41.For the Mycenaean collapse, see herein, chapter 9, pp.270–273.For classical Greece, see herein, chapter 6, pp.188–199.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罗马世界内部的变动: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帝国西部可能已经代表了那个时代不平等的顶峰。
[2] State collapse: herein, chapter 9, pp.264–269.Plague: herein, chapter 11, pp.319–326.
[3] For what seems to me an overly imaginative attempt to track the late and post-Roman decline in income inequality, see Milanovic 2010: 8 and 2016: 67–68.For conditions in Constantinople in this period, see Mango 1985: 51–62; Haldon 1997: 115–117.
[4] Bekar and Reed 2013对英格兰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的模型中,这些因素能够使得土地基尼系数增加4倍,从0.14变成0.68,然而土地比例或者人口增长产生的效应很小;See also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51–53 for a model of a peasant holding of fifteen acres that barely allowed tenants to make ends meet.Rents and plots: Grigg 1980: 68;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50–51。
[5]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55–58.
[6] Byzantine inequality: Milanovic 2006.England and Wales: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 (c.0.36), based on Campbell 2008.The next-oldest estimate, for Tuscany in 1427,postdates the Black Death but is higher (0.46), which is what we would expect from a heavily urbanized environment.Wealth concentration in Paris and London: Sussman 2006, esp.20 table 9, for wealth Ginis (inferred from tax payments) of 0.79 in Paris in 1313 and 0.76 in London in 1319.如果没有把非常穷的人从基础性的税收记录中忽略,巴黎的基尼系数可能会更大。
[7] See herein, chapter 10, esp.pp.300–311.
[8] Scholarship on this transformation is vast.For a very high-flying bird’s-eye view,appropriate in this context, see Christian 2004: 364–405.The contributors to Neal and Williamson 2014 survey the many-faceted rise of capitalism, and Goetzmann 2016 emphasizes the role of finance in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当然,很明显,“获取”依然是今天世界大部分地方致富和不平等化的一个有效的战略:参见Piketty’s 2014: 446提到的“偷盗”也是一种积累机制,其例证是赤道几内亚的专制统治者。
[9] For this last point, see most recently Alfani 2016: 7, with references.在下文中,一种叙述的模式,即突出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和趋势,看起来最适用于不同的本地数据集的局限性和特点,也避免了由统一的表格传递出来的关于准确度的似是而非的印象。
[10] Florentine catasto: van Zanden 1995: 645 table 1.(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among 522 merchant families in Florence in 1427 shows a Gini coefficient of 0.782: Preiser-Kapeller 2016: 5, based on http://home .uchicago.edu/~jpadgett/data.html.) Tuscany: Alfani and Ammannati 2014: 19 fig.2.Piedmont: Alfani 2015: 1084 fig.7.
[11] Germany: van Zanden 1995: 645–647, esp.647 fig.1 on Augsburg, and herein, chapter 11,pp.336–337.Netherlands: van Zanden 1995: 647–649;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46 table 3.10.England: Postles 2011: 3, 6–9; 2014: 25–27.Soltow 1979: 132 table 3 calculates a wealth Gini of 0.89 for Copenhagen in 1789.Urbanization rates: De Vries 1984: 39 table 3.7.
[12]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61 (urbanization);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23–25(general conditions), 42, 46, 53–54 (capital and labor).
[13]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38 table 3.6, 39 (Leiden); van Zanden 1995: 652–653;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35 table 3.4 (rental values); cf.139 for a Gini of 0.65 in 1808.Fifteen towns: Ryckbosch 2014: 13 fig.1; cf.also 13 fig.2 and 14 fig.3 for time trends by city,which show somewhat more variation over time.The Gini for house rents in Nijvel rose from 0.35 in 1525 to 0.47 in 1800: Ryckbosch 2010: 46 table 4.在斯海尔托亨博斯,1500—1550年之间,平滑后的名义房租不平等,经过家庭人数和价格的调整之后,掩盖了实际不平等的上升。
[14] SSoltow and van Zanden 1988: 40 (stalled growth); Ryckbosch 2014: 17–18, esp.18 fig.5,22 (north/ south), 他总结到,荷兰和佛兰芒的不平等程度在出口奢侈品和服务的技能密集型阶段比较低,而在低工资的大规模标准化出口生产时期比较高(23);Alfani and Ryckbosch 2015: 28 (taxes); van Zanden 1995: 660 table 8;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43–44, 47 (wages)。
[15] Alfani and Ammannati 2014: 16 table 3 (Tuscany), 29 table 4 (wealth shares); Alfani 2015: 1069 table 2 (Piedmont); Alfani 2016: 28 table 2 (Apulia); 12 fig.2, 13 (multiple of median value).Two Sicilian data sets also point to rising wealth inequality: Alfani and Sardone 2015: 22 fig.5.
[16] Alfani 2014: 1084–1090; Alfani and Ryckbosch 2015: 25–30.
[17] Fig.3.2 from Alfani and Ryckbosch 2015: 16 fig.2b and Alfani and Sardone 2015: 28 fig.9.Cf.also Alfani 2016: 26 fig.4 and 30 fig.6 for similar trends for top wealth shares and a “richness index.” Alfani and Ryckbosch 2015: 30 offer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different causes of rising inequality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For England, see Postles 2011: 3, 6–9; 2014: 27.
[18] Spain: A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13.Fig.3.3 from tables S2 and S4 (http://onlinelibrary .wiley.com/doi/10.1111/j.1468–0289.2012.00656.x/suppinfo).Madrid:Fernandez and Santiago-Caballero 2013.在加泰罗尼亚,在1400—1800年间,顶层1%和顶层5%收入的人群的财富比例或者上升或者保持相对稳定,同时总体的财富基尼系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García-Montero 2015: 13图1, 16页图3。Santiago-Caballero 2011 documents fairly stable inequality in the province of Guadalajar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xcept for a modest dip late in this period associated with land reform (see herein,chapter 12, p.355).For falling European real wages, see herein, chapter 10, pp.301–302.
[19] France: The classic study is Le Roy Ladurie 1966, esp.239–259, and also 263–276 for falling real wages.Portugal: Reis, Santos Pereira, and Andrade Martins n.d., esp.27 fig.2, 30–32,36–37 figs.5–6.在1770年,波尔图的不平等水平比其在1700年的水平低,也低于1565年里斯本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要比1565年的更低,但是在大城市要比1565年和1700年的水平高一些(27页 图2)。Their work is based on income tax data, improving on the survey of material from 1309 to 1789 by Johnson 2001, which suggests a similar trend.Little is known about Central Europe: see Hegyi, Néda, and Santos 2005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elite wealth proxied by the number of serfs in Hungary in 1550.
[20]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1811年的那不勒斯被认为表现出一种达到0.28的非常低的收入基尼系数,这看起来很值得怀疑。
[21] Extraction rates: for the concept, see herein, appendix, p.447.随着人均GDP停滞甚至收缩,榨取率在托斯卡纳的皮埃蒙特和南部低地国家中上升了:Alfani and Ryckbosch 2015:24。在荷兰和英格兰,未调整的榨取率(相对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在前者下降,而在后者的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背景中波动着,经过不断上升的社会最低生活需求调整的榨取率则保持不变:Milanovic, Lindert,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 Milanovic 2013: 9 fig.3。For real wages, see herein, chapter 10, pp.301–302.“Real”inequality was higher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1800 than it had been in 1450 or 1500: Hoffman, Jacks, Levin, and Lindert 2005: 161–164, esp.163 fig.6.3(a–c).I note in passing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could also translate to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terms of body height: Komlos, Hau, and Bourguinat 2003: 177–178, 184–185, on France.
[22] Canbakal and Filiztekin 2013: 2, 4, 6–7, 8 fig.7 (urban Ginis), 19 fig.9 (top decile), 20 fig.10 (rural Ginis), 22.For a more detailed study of one of these cities, Bursa, see also Canbakal 2012.Pamuk forthcoming surveys developments after 1820.
[23] For Han inequality, see herein, pp.63–69.Developments in the Period of Disunion are summarized by Lewis 2009a.
[24] For the Tang, see herein, chapter 9, pp.260–264.For later dynasties, see very briefly herein,pp.69–71.China in 1880, India in 1750 and 1947: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3 table 2.关于亚洲不平等状况的正式研究依然比较缺乏。Broadberry and Gupta 2006: 14 table 5, 18 table 7 find that real wages of unskilled workers in the Yangzi Delta were lower in the mid-Qing period (1739–1850) than they had been under the late Ming(1573–1614), that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India there were lower in 1874 than they had been under the Mughals, and that in southern India they were lower in 1790 than they had been in 1610.Although all this points to rising inequality, these findings would need to be more fully contextualized to provide more certainty.For Japan, see herein, chapter 4, p.118.
[25] See herein, pp.58–59 (pre-Columbian inequality), and herein, chapter 11, pp.317–319(epidemics) and chapter 13, pp.378–382.Fig.3.4 is based on Williamson 2015: 35 table 3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6–297 table 12.1, adjusting Williamson’s inequality levels to bring them in line with the latter’s lower income Ginis and account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Aztec and Inca empires and the effects of epidemic mortality.
[26] Wealth: Lindert 2000b: 181 table 2.顶层的收入集中如此极端,以至顶层的4%群体的份额从43%下降到18%,前5%的总份额则从82%上升到87%。Landownership: Soltow 1968: 28 table 3.Income inequality up to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dert 2000b: 18–19, 24.
[27] For the notion of a “Kuznets curve” (for which see herein, chapter 13, pp.369–372) during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see Williamson 1985 and 1991, esp.64 table 2.5, forcefully and to my mind compellingly challenged by Feinstein 1988.Wage dispersion: Williamson 1991: 61–62 table 2.2, based on six unskilled and twelve skilled occupations, cf.also 63 table 2.3.Feinstein 1988: 705–706表明,这12个技能型职业的曲线其中有7个显示出名义年收入的逐渐上升,有5个表现出不稳定的波动。他总结道:“技能型劳动力的工资结构一个世纪以来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前半叶没有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后半叶也没有平等性矫正。”(710; and see also Jackson 1987).For a critique of house dues,see 717–718.Top income shares: Williamson 1991: 63 table 2.4, with Feinstein 1988:718–720.Social tables: Feinstein 1988: 723 table 6, and see also Jackson 1994: 509 table 1:0.47–0.54 in 1688 (without and with paupers), 0.52–0.58 in 1901 and 1903, and 0.48 in both 1867 and 1913.Jackson 1994: 511 deems it unlikely that inequality peaked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Soltow 1968: 22 table 1 had already arrived at a similar conclusion of broad stability in this period.Lindert 2000b: 21–24 shows that trends in English real inequality acros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pend on which measure we select.This holds true regardless of evidence for stagnant real wages of English work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rising ones in the second half: see Allen 2009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The observation that “real”—i.e., class-specific—ine- quality declined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ffman, Jacks, Levin, and Lindert 2005: 162 fig.6.3(a)) is likewise inconsistent with a scenario of rising followed by falling inequality.The evidentiary weakness of any claim that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followed aKuznets curve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its continuing popularity of this notion in post-1988 scholarship: see, e.g., Williamson 1991; Justman and Gradstein 1999: 109–110;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1192–1193; 2002: 187 table 1; and, most recently, Milanovic 2016: 73 fig.2.11, 74–75, who references Feinstein’s critique in an endnote (248–249 n.25).
[28] Italy: Rossi, Toniolo, and Vecchi 2001: 916 table 6 show a gradual decline in Ginis and top decile income shares between 1881 and 1969, whereas Brandolini and Vecchi 2011: 39 table 8 present various metrics that strongly indicate stability between 1871 and 1931.France:Piketty, 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 2006: 243 fig.3, 246 fig.7; Piketty 2014: 340 fig.10.1.Spain: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8: 298 fig.3; see herein, chapter 13, pp.372–373.
[29] Prussia: Dell 2007: 367 fig.9.1, 371, 420 table 9I.6 (income shares).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几乎没有任何下降,1900—1913年之间,大约只有0.8%,要比之前预计的少一些。早期研究计算出来的1896—1900年或1901—1910年与1913年之间相比,下降程度为1%~2%:Morrison 2000: 234, and see 233, 257, also for Saxony.Dumke 1991:128 fig.5.1a finds rising inequality and capital shares from 1850 to 1914.Prussian Gini:Grant 2002: 25 fig.1, with 27–28.Netherlands: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145–174,esp.152, 163–165, 171.They note the absence of any Kuznetian wage dispersion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as skills premiums fell: 161–162, 174。
[30] 1870年收入分配的隐含基尼系数比较高,位于名义极端值的0.53~0.73的任何位置。给定那个时候丹麦人均GDP为2000美元,0.63的中间值可能意味着3/4的榨取率,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类似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前现代社会。只有在基尼系数估计值下限的数值才能与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值相当,这是非常不平等的开始。此外,在0.55左右的一个合理的较低的1870年基尼系数,能够在1903—1910年的估计值的置信区间内被发现,从而不可能排除1870—1910年间不平等没有显著变化的原始假设。See Atkinson and Søgaard 2016: 274, euphemistically noting the “limited data coverage” for the period from 1870 to 1903.Implied Gini for 1870: 277 fig.5.For 1789: Soltow 1979: 136 table 6, from which Atkinson and Søgaard 2016: 275 infer an extravagantly high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 of 30 percent.丹麦的人均GDP在1820年的时候在1200美元左右,这可能对应一个高达0.75的收入基尼系数,大概比1789年的还要低一些。
[31] Wealth inequality: Soltow 1979: 130 table 2, 134, with Roine and Waldenstrom 2015: 572 table 7.A2(for a drop in the top 1 percent share from 56 percent in 1789 to 46 percent in 1908; but cf.579 table 7.A4 for unchanged top deciles across this period).
[32] Norway: Aaberge and Atkinson 2010: 458–459 (who note that the early data are poor: 456);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72 table 7.A2 (but cf.579 table 7.A4 for a top 10 percent wealth share in 1930 that was higher than it had been in 1789).Cf.also Morrison 2000:223–224 for gradual leveling in two Norwegian counties between 1855 and 1920, based on much earlier work by Soltow.Sweden: WWID; Soltow 1985: 17; Söderberg 1991; Piketty 2014: 345 fig.10.4.
[33] For the colonial period, see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4: 4, 28–29.For 1774: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36–41, esp.38 table 2–4 for an income Gini of 0.44 and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s of 8.5 percent for all households and of 0.41 and 7.6 percent for free households.At 0.37 and 4.1 percent, New England was exceptionally egalitarian.Revolutionary period: 82–90.The urban/rural wage premium for unskilled male earnings fell from 26 percent to 5 percent and from 179 percent to 35 percent for average urban/rural earnings.The premium for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relative to urban male unskilled earnings collapsed from 593 percent to 100 percent.Rising inequality up to 1860:114–139.Disparities grew both between free and slaves and among the free population.For Ginis and income shares, see 115–116 tables 5–6 and 5–7.Proper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122 tables 5–8 and 5–9.
[34] For the period 1860 to 1870, see herein, chapter 6, pp.174–179.For 1870–1910: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171–193, esp.172 (top income shares about 1910, with WWID), 192–193.Smolensky and Plotnick 1993: 6 fig.2 (not referenced by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but used by Milanovic 2016: 49 fig.2.1, 72 fig.2.10)从已知的收入基尼系数,即顶层5%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和1948—1989年间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推出1913年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大约在0.46,如果这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1870—1913年间整体收入不平等的显著下降。此外,这一过程的有效性和这些年份的估计值之间的可比性依然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似乎与这一时期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明显上升对立。Wealth shares: Lindert 1991: 216 fig.9.1; Piketty 2014: 348;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572 table 7.A2.Largest fortunes: Turchin 2016a: 81 table 4.2.
[35] Latin American Gini estimates: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120 table 3.15;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6–297 table 12.1.Rodríguez Weber 2015: 9–19 offers a more nuanced account for Chile.Using (land) rent/(urban) wage ratios, Arroyo Abad 2013: 40 fig.1 finds net increases in inequality in Argentina and Uruguay between 1820 and 1900 but not in Mexico and Venezuela.Japan: Bassino, Fukao, and Takashima 2014; Bassino, Fukao,Settsu, and Takashima 2014; Hayami 2004: 16–17, 29–31; Miyamoto 2004: 38, 43, 46–47, 55; Nishikawa and Amano 2004: 247–248.For growing inequality during modernization,see herein, chapter 4, p.118.
[36] 基于一个更为受限的数据集,我的调查证实了阿尔法尼的观察,即皮凯蒂描写的19世纪的财富集中过程“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更长期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Alfani 2016: 34)。
[37] 共产主义政权在1950年拥有25.6亿世界人口中的8.6亿。Income shares: WWID,summarized by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493 fig.7; and see herein, chapter 5, pp.130–137 for more detailed analysis.(我们只有英国1%顶层收入群体收入占比的零星数据,它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收缩过程,1937—1949年的1/3的下降就可以反映出来。从1913年或者1918—1949年的0.1%和1%顶层收入群体的损失率之间的比率,我们可以推断1913年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大约为25%,并且到1949年整体的下降程度为略微超过一半。)For Russia and East Asia, see herein, chapter 7, pp.221, 227.Wealth shares: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72–581 and esp.539 fig.7.19, reproduced herein, chapter 5, p.139.Capital/income ratios: Piketty 2014: 26 fig.1.2 (reproduced herein, chapter 5, p.140), 196 fig.5.8; data appendix table TS12.4.(For criticism of the highly conjectural global estimate, see Magness and Murphy 2015: 23–32; but the overall trend is quite clear.)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leveling process, see herein, chapter 15, p.405; for 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effective inequality levels, see herein, in the appendix.By some multidimensional inequality measures, contemporary Scandinavi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as egalitarian as forager societies: Fochesato and Bowles 2015.For a very brief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up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 herein, chapter 14,pp.389–391.
日本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38年时,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申报的总收入中占19.9%。然而在随后的7年,这个份额下降了2/3,一路降至6.4%。其中,这个顶层群体中最富有的1%群体承担了超过一半的损失:同期,他们的收入份额从9.2%锐减至1.9%,减幅接近4/5(图4.1)。
尽管发生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迅速且巨大,但与精英阶层在财富方面遭受的更引人注目的破坏比起来,又逊色不少。就日本规模最大的1%资产而言,其公布的实际价值在1936—1945年间缩减了90%,1936—1949年缩减了近97%。最顶层的0.1%资产损失得更多——实际价值分别缩减了93%和98%以上。以实际价值计算,1949年时一个家族跻身顶层的0.01%家族之列(万里挑一)所需要的财富,若退到1936年,仅够其进入前5%家族之列。股票也严重缩水,以至以前仅仅算得上殷实的财富水平,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尽管统计数据的不连续性使得我们很难对日本不平等缩减的总体情况做出精确的估计,但它们确实表明,日本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介于0.45~0.65之间,降至1950年代后期的0.3左右;这一下行趋势是确凿无疑的,它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矫正。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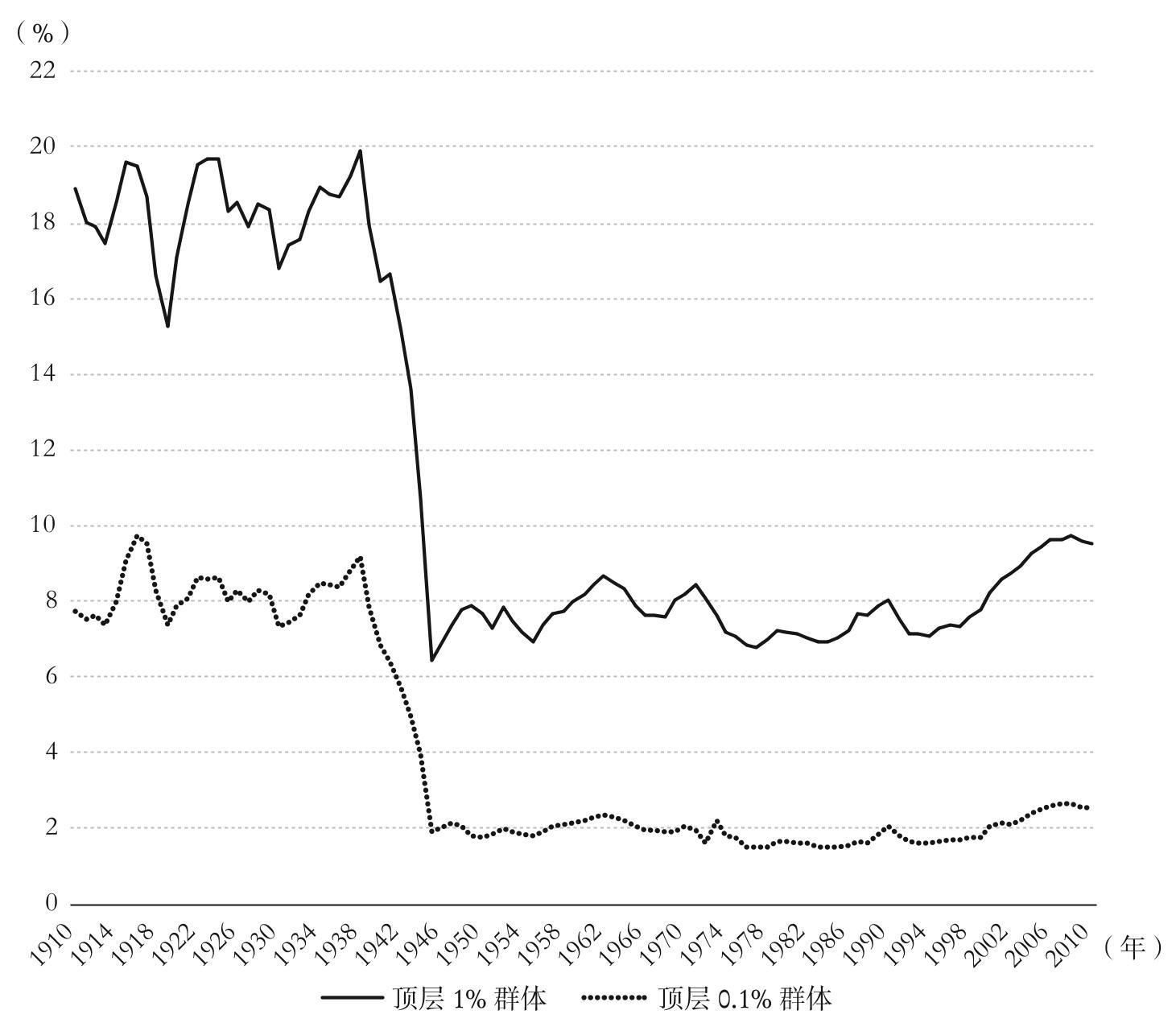
图4.1 日本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1910—2010年(以百分数表示)
就精英阶层的收入而言,日本一下子从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堪比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夕的美国——“顶层1%群体”处于高水位的社会,变成了类似于今天的丹麦的社会,后者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来看是当世最平等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精英阶层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毁于一旦。但日本人从未有过“向丹麦看齐”的想法。它所做过的仅仅是卷入,或者依据我们的定义来说——发动了“二战”:先是企图控制中国,继而建立起一个西起缅甸,东至密克罗尼西亚环礁,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赤道以南所罗门群岛的殖民大帝国。在其鼎盛时期,这个帝国所控制的人口据说与同期的大英帝国大致相当——接近5亿人,或者说约为世界人口的1/5。 [2]
为了维持这一耗资巨大的冒险,日本军队的规模从1930年的25万人到1945年夏季时的500万人,增加到20倍。也就是说,不论年龄大小,每7个日本男性中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50万日本军人战死。战争最后9个月,美国投掷的炸弹为日本带来了致命和毁灭性的打击,共有70万居民丧生。在这种极度恐怖的环境下,两颗原子弹总算是为日本人长期的劳累、苦难与毁灭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大战中全面失败后,日本被几十万美国军队占领,并被迫实施了旨在扼制其军国主义野心的全方位制度改革。
这些戏剧性的进展,不只为一次超乎寻常的大矫正过程提供了背景,它还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原因。全面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并且,正如许多最近出现的研究所言,这一结果绝不仅限于日本。卷入“二战”乃至之前“一战”的其他主要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尽管在程度上并非总是这般极端。它也发生在几个并未卷入战争的邻国身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20世纪出现的两大矫正机制之一。另一个矫正机制是能够造成结构性转变的革命:然而,由于这些革命是由世界大战推动的,因而全面战争又是唯一和最终的原因。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矫正四骑士的比喻来说,战争和革命堪称一对携手并进的孪生子。
日本为战争驱动型的矫正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因此,接下来我会对这个国家在战争期间及被占领时期的情况做出更为细致的描述,以便辨别出那些共同导致了该国财富损毁和不平等大幅缩减的各式各样的因素。然后,我还会通过简要地考察各国在战时的经历,战争对后续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战争对促进一体化和民主化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等,从短期和中期的视角对与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矫正过程,做出更系统、范围更广泛的评价。在后面的各章中,我要探究的是,由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带来的矫正在历史上能够被追溯到多远,那些历史上更为普遍的其他类型的战争会造成何种影响,以及最后,内战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将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暴力曾经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不平等程度施加过影响:唯有那些动员最为广泛的军事活动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世界开放之后,不平等程度呈不断上升之势。与更早时期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时,各省的数据表明,按当时的国际标准判断,个人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是比较低的。没有证据显示薪酬不平等在德川时期扩大了,相反倒是有证据表明,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按城市工资计算,技术工人的额外收入呈逐步下降趋势。果真如此的话,那将意味着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了,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是不断缩小的。在这一阶段晚期,地主们发现他们在有关由谁来控制日益增长的剩余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受制于不变的土地税率,他们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商人和农民的挑战。由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国际贸易额大幅缩减,更普遍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也不能通过商业活动获利,而这同样有助于遏制不平等。 [3]
这一切都随着日本加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行列和启动快速的工业化而发生改变。尽管缺少可靠的数据,但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之后该国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和上层收入份额都上升了。工业化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之后加速发展。与欧洲之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交往带来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即便在价格膨胀导致实际工资缩水的情况下亦是如此。随着“一战”的爆发,从大宗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份额上升,收入增长速度也开始高于工资增长速度。相应地,不平等在“一战”期间也开始增加。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富精英一直都在高歌猛进:地主、股票持有者以及公司执行官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巨大。股权高度集中,且他们因为慷慨的分红而收益颇丰。公司高管往往也是大额股份的持有者,并能够获取很高的薪酬和红利。低税率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护,并促进持续的财富积累。 [4]
这一安逸的局面在1937年7月因日本入侵中国而突然中止。随着从最初的战事扩展到对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无节制入侵,日本不得不以加速之势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方面。随着1940年9月之后逐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及1941年11月对美国、英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起全面进攻,日本的赌注进一步提高。在太平洋战争的头6个月里,日本军队遍布从夏威夷群岛和阿拉斯加到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区。截至1945年,大约有超过800万的日本男性,即日本1/4的男性人口,曾在军队服役。武器生产在1936—1945年间实际上增长了21倍,政府支出从1937—1941年增长了一倍多,随后的4年又增长一倍。 [5]
这一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度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战争期间,政府管制、通货膨胀以及物质损毁,矫正了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三种机制中的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国家干预逐步创造了一种徒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外表的计划经济。最初实施的紧急措施不断扩大并日益制度化。1932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在那里建立的指令性经济,提供了一个样板。1938年春季颁布的《国家全面动员法》赋予了政府要求日本经济服务于战争(它很快就升级成了全面战争)的广泛权力:雇用和解雇决定工作条件、生产、分配、迁移和商品价格,以及解决劳动纠纷的权力。1939年颁布的《限制企业分红和资本流通条例》,对红利增长施加了限制。农业租金和部分价格被冻结,工资和土地价格开始受到管制。1940年公司执行官的红利受到封顶限制,随后一年当局又固定了租金收入。在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4年以及1945年里,针对个人和企业征收的所得税几乎都有提高。1935—1943年间,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增加了一倍。政府干预股票和债券市场,以牺牲企业股票和债券为代价发展战争债券,从而导致了更低的收益率。大幅度价格膨胀连同城市和土地租金以及地价的固定化政策一起,导致了债券、存款和地价的下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征用了所有排水量超过100吨的私人船只,且几乎没有返还:每5艘商用船中的4艘都消失在了战争中。1943年颁布《军需企业法》后,按规定,那些被官方指定为军需企业的公司必须设置直接听命于政府的生产监督官,由其决定设备投资、工作安排和资金分配,利润和分红也由国家确定。从1943年开始,政府强力推进了全面偏向军需的生产:不可信的未来补偿承诺充当了唯一的诱饵。1944年政府权力进一步膨胀,一些贸易被国家化。一项调查列举了1937—1945年间日本政府推出的大约70种不同的经济控制——包括配额、资本控制、工资控制、价格控制和土地租金控制在内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措施。 [6]
原本由几个富有家族牢牢控制着的联合大企业财阀体制开始遭到削弱。由于靠富人进行的企业储蓄和投资被证明不能满足战时工业膨胀的资本需要,所以必须从这些传统的封闭小圈子外部筹措资金,日本工业银行也缩减了私人金融组织的市场份额。由于以往企业股票的主要所有者同时也把持着高层管理职位,所以资本化的增加和外部借贷提供了联结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一个直接纽带,而这会带来财富积累的不利结果。更普遍地说,战争压力催生了这样一种新观念,即公司不应该被股票持有者单独占有,而应该由包括每个成员在内的共同组织所有。这一信条使得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化行为受到鼓励,工人因此被赋予了包括利润分享在内的更多权利。 [7]
战时施行的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为后来美国占领时期实施的全面土地改革埋下了伏笔。战前,地主(大多数是中等富有者)占有所有土地中的一半,所有农民中的1/3是其承租者。战争期间,农村的贫困已经触发了一些冲突和动荡,但改革的尝试是迟疑不决的。这一局面随着1938年出台《农业调整法案》而发生改变,该法案力图鼓励所有者出售已出租的土地,并允许强制性地购买未开垦的土地。1939年颁布的地租控制令将地租冻结在当时的水平上,并赋予了政府勒令削减地租的权力。1941年的地价控制令将土地价格固定在1939年的水平上,同年颁布的土地控制令使得政府拥有了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的权力。1942年的食品控制令,使得政府开始有权决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所有超过个人消费所需的稻米都必须卖给国家,所有超过个人所需的地租都必须转换成短期国库券。在缺乏价格激励的情况下,给予稻米种植者的补贴不断增加,以鼓励其生产。这使得主要生产者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增长,地主收入遭到侵蚀,此一差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可观的矫正效应。实际的农业租金在1941—1945年间减少了4/5,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4.4%降低到1946年的0.3%。各种有关没收、征用土地的倡议曾四处流传,所以地主的状况本来有可能更糟,但这些倡议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 [8]
工人不仅从租金控制、国家补贴以及政府对商业管理不断强化的干预中获益,而且还从政府为保证入伍者和工人身体状况以及减少市民不安定情绪而实施的扩张性福利供给中获益。1938年福利部门一组建起来,便立即成了推进社会政策的主要力量。它启动了部分由国家出资的健康保险计划,同减贫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在1941年之后大幅扩张。为抑制消费,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补贴计划,同时在1941年破天荒地实施了公共住房计划。 [9]
第二种矫正力量,即通货膨胀,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加速。消费价格在1937—1944年间上升了235%,接着又在1944—1945年的短短一年间跳至360%。这使得即便是在地主的实际收入因租金控制而遭受侵蚀的情况下,债券和股票价值仍然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10]
与欧洲战区不同,在日本,第三个矫正力量即资本方面的物质性破坏,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开始起作用,尽管其航运业很早就遭到了打击。到1945年9月时,该国实物资产总量中的1/4已损耗殆尽。日本损失了80%的商用船舶、25%的建筑、21%的家用器具和私人物品。战争最后一年,仍在生产的工厂数量及其雇佣劳动力的规模,缩减近半。损失程度因行业而异:钢铁业损失甚小,但纺织业中的10%、机器制造业中的25%、化工业中的30%~50%,都停止了生产。这些损失绝大多数都是由空袭造成的。根据1946年的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报告,盟军当时已向日本投掷了160800吨炸弹,尽管比对德国的轰炸少了1/8,但由于日本防御更差,所以反倒更成功。1945年5月9—10日夜间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据保守估计,在大约1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造成了近10万居民丧命,超过25万栋的建筑和屋舍损毁,然而,这仅仅是显著的一例而已;5个月之后,广岛和长崎的遭遇同样如此。该报告的编写者估计,被轰炸的66个城市有40%的建成区遭到损毁,全国大约30%的城市人口丧失家园。尽管这给地产所有者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但其总体影响不应被高估。由于重化工业在战时的急剧扩张,1945年残留下来的生产设备量超过了1937年时的可用量。并且,除了造船业这个例外,实物损毁主要发生在战争的最后9个月,在此之前,社会上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就已经开始加速下降(见图4.1)。盟军的轰炸仅仅是使已然之势进一步加速而已。 [11]
资本收益在战争期间几乎荡然无存:租金和利息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是1/6,在1946年仅为3%。1938年时,顶层1%群体收入的1/3由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构成,剩下的部分则是商业和雇佣收入。到1945年,资本收入份额已降到1/8以下,工资收入份额降至1/10;商业收入成为(以往的)富人们开支的最重要来源。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看,股息和工资,在不断增强的政府控制的影响之下,遭到的打击最严重。放贷取息者和拿高薪的企业执行官,作为一个阶层几近破产。这种败落的景象,对处在1%人口最顶端的那些人来说尤为惨重。
与此同时,第二富有的收入群体并没有遭到任何可比的挤压。在收入阶梯中处于第95~第99百分位之间的那些家庭(收入水平紧随顶层1%群体之后的4%的富人),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下降,并且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稳定在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大致持平的水平,换言之,其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12%~15%。尽管大多数人都遭受了损失,但就相对值而言,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是那些最富有的日本人:“二战”之前,顶层“1%”群体的总收入一直都在第二富有的4%群体总收入的1.5倍左右,但1945年之后再也没能达到多于后者一半的水平。由此说来,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换来的是95%的非精英人群收入份额的上升,即从1938年占国民收入的68.2%上升到1947年占国民收入的81.5%,升幅达到20%。这确实是一次壮观的转变,它使得95%国民的收入份额,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堪比2009年时美国的水平上升到同今天的瑞典大致相当的水平。 [12]
然而,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只是矫正过程的一部分。日本在大的参战国中或许有其独特之处,这是因为它所有被观察到的净收入减少都发生在“二战”期间,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主要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战后。然而,正如其他的国家一样,长期来看,导致收入和财富分散化的是战后实施的平等化政策。就日本而言,所有这些政策都能被证明是战争的直接后果。当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承认“战争形势并没有朝着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以及时局已到“承受不可承受的结果”之时——无条件投降以及被盟军占领,日本经济已经满目疮痍。原材料和燃料短缺已导致生产瘫痪。1946年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37年的低了45%,进口额仅为1935年的1/8。随着经济的复苏,整整一揽子的政策以及战争引起各种相关效应,使得战时已经出现的收入压缩局面得以维系,甚至使财富分配变得更为均等。 [13]
战争结束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自1937—1945年间上升14倍之后,又在1945—1948年间以快得多的速度一路飙升。虽然报道出来的各项指数多有不同,但依据其中的一种度量方法,1948年时的消费者价格比日本入侵中国时高出了1800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收入剩下的部分蒸发了! [14]
公司和地主是激进重组的目标对象。美国占领日本政府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消除财阀、劳动民主化和土地改革,这些举措会连同惩罚性的累进征税一起实施。其最终的目标不仅是消除其发动战争的物质潜能,而且是消除可感知到的帝国主义侵略根源。经济改革构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旨在重塑日本制度结构的根本民主化变革的一部分:新宪法、妇女的选举权、法院和警察制度的彻底变革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正是战争导致了日本被他国占领。 [15]
政府干预毫不隐讳地致力于经济矫正,这被视作达到预想结果 [01] 的一种手段。美国占领当局接到的题为“日本经济制度民主化”的“基本指令”,敦促其推进一种“收入及生产和贸易手段所有权的更广泛分配”。为了缔造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占领当局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新政的政策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43年和1945年,美国的研究者曾评价指出,日本产业工人和农民在财富分配方面所占的较低份额抑制了国内消费,并引发了对外经济扩张。现在实施以更高工资水平为特征的劳动重组,正是为了对之做出补救,它将提振国内消费并促进去军事化。经济民主化和矫正本身并非目的,其深层政策目标在于,通过重构有可能导致对外侵略的经济特征来防范军国主义。归根结底,战争及其后果要再次为这些变化负责。 [16]
占领者以税收为利器痛下重手。1946—1951年间,他们针对资产净值征收了高额和累进的财产税,免征额低,最高边际税率达到90%。针对资产而不是针对收入抑或仅仅针对不动产征税,其没收充公的本质昭然若揭。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征税旨在重新分配私人财产,使财富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下层阶级手中,以提升后者购买力。一开始,其征收对象覆盖了1/8的家庭,并最终将5000个最富有家庭70%的财产以及全部应税资产的1/3,转移到国家手中。一段时期里,在总体税负已经较低的情况下,征税特别指向富人。根本原则是再分配,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同样是1946年,许多银行存款先是被冻结,接着又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两年后那些超过某一门槛线的存款干脆被抹掉。 [17]
占领当局对财阀,即家族拥有的商业联合集团,抱着十分消极的态度,把它们视为战争年代军国主义领导集团的亲密伙伴,以及更一般地视其为一种使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半封建关系永久化的力量,这种关系既使得劳工工资被压低,又有利于资产阶级牟取暴利。最大的财阀最终被解散,它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被摧毁。(旨在重组数百家商业机构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后来因“冷战”政策调整而搁浅。)这些财阀家族被迫出售了手中42%的股票,这导致了企业持股比例的巨幅下降。在1947年面向全国开展的高级管理层整顿运动中,大约有2200名来自632家公司的高管被遣散,或者在预期到会被遣散的情况下主动选择退休。这样,以前那种企业由资本家牢牢掌控的体制就被清除掉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其1948年的新年文告中这样宣称:
联合政策要求终结过去那种允许你们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归少数封建家族所有和控制,并服务于其排他性利益的体制。 [18]
最初的干预计划非常严厉。1945年和1946年时,占领政府者曾考虑过一项计划,即撤除加工制造和能源生产设备,使生活标准维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或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水平,并将所有高于该门槛线的东西用作战争赔偿。尽管作为对新出现的“冷战”现实的反应,这些政策很快便发生了变化,但大量进攻性的措施事实上还是得到了实施。军火制造厂以及相关的生意被没收充公,作战争赔偿之用。1946年7月,美国人以“战争不是一桩赚钱的生意”为由,叫停了战争赔偿支付,未付款项被清除。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和银行收支平衡压力。许多公司在随后几年里都面临着清偿问题。另一些公司为了生存下来,用光了保留基金、资本和股权,甚至向债权人转嫁负担。 [19]
战败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损失。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因为投资台湾地区、韩国、孟加拉国等殖民地而出现了资本外流问题。战争期间,日本公司在殖民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占领区的经营越发具有侵略性。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平协定后,日本失去了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海外资产——在此之前这些资产的大部分已经被不同的国家夺取。 [20]
金融部门彻底毁灭。到1948年时银行亏损已经非常大了,以至要弥补它们,必须抹掉所有的资本收益和留存收益,并砍掉银行90%的资本金,外加注销某一门槛线之上的存款。股票持有者不仅招致了巨大的损失,甚至还被禁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购入新股。结果是资本收入不复存在。1948年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加在一起,占顶层1%群体总收入的比重不超过0.3%,这个数字在1937年是45.9%,在1945年是11.8%。 [21]
劳工联合是一个关键因素。战前的工会参与率不超过10%,1940年时原有的工会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工人爱国产业协会。建立这种形式的劳工组织,最初是为了激发工人为战争提供支持的劳动积极性,但客观上又为占领时期建立一种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工联盟准备了条件。1945年美国军队刚一进驻日本,占领当局便通过修改战前制订的一项未获通过的计划,形成了有关劳动联合的法案。年底,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人因此被赋予组织、罢工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参与率一路狂飙:1946年时,加入劳工联盟的工人占40%,1949年更是接近60%。高工资收入者获益良多,创建于战争期间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使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事实证明,建立强调工龄工资、工作保障的劳工联盟,有助于形成合作性的产业联系——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矫正的视角来看,它有助于人们对一种以年龄、需要、生活水平、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的新型工资结构达成共识。针对新入职者设立的最低生活工资,随年龄、资历和家庭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对生活工资所做的经常性调整,缩小了最初存在于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鸿沟。 [22]
最后,土地改革是占领当局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他们把地主所有制视为一种必须消除的大恶。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提出,重新分配土地是使日本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关键,而此前日本军方已使贫穷的农民相信海外侵略是使他们脱贫的唯一出路:不推行土地改革,农村可能继续成为军国主义的温床。再一次地,其深层依据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以太温和为名否决了一份由日本农业部设计并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通过的土改方案,1946年冬,一份修订后的方案成为正式的法律。与定居地主所拥有和出租的所有超过1公顷的土地一样,非定居地主(那些居住地与土地所在地不是同一个村庄的地主)拥有的全部土地被强制卖出。所有者自己耕种的超过3公顷的土地,若被认定为无效率经营,也可能被包括在内。补偿的标准刚一确定,很快就因通货膨胀肆虐而遭到破坏。各类租金也是一样,它们被要求按1945年底的水平以现金来支付,但最终也随着通货膨胀而逐渐被破坏。同时发生的土地实际价格的下降也毫无二致:1939—1949年间,相对于稻米,稻田的实际价格下降为1/500,相对于烟草价格,大约下降为一半。改革覆盖了日本1/3的农用土地,进而牵涉半数的该国农村住户。战前用于出租的土地占到了全部土地的一半多,1949年降至13%,1955年降至9%,而拥有并自己耕种土地的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31%变成70%,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无地佃农几近消失。农村城镇的收入基尼系数从战前的0.5降到战后的0.35。尽管这场改革以战时的措施和观念为基础,但以这般巨大的规模实施,直接源于被占领这一事实。麦克阿瑟将军曾以其特有的谦逊声称,这一计划“或许是史上最成功的土地改革计划”。 [23]
从1937年入侵中国到1951年签署和平协定,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及随后被占领的那些年,日本人收入和财富的来源与分配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顶层收入份额的巨幅下降,以及本章开始时所观察到的巨额财富规模的戏剧性崩溃,首先要归因于资本收益的下降,并且,受这一因素影响的远远不是那些很富有的人。在总资产中占9%的那部分最大规模的资产,其内部构成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动。1935年时,股票、债券和存款在这部分资产中大约占一半,到1950年时,它们的占比下降到1/6,与此同时,农用耕地的占比也从接近1/4下降到1/8以下。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所遭遇的全部下降,以及就绝对值而言,其资产的实际价值所遭遇的几乎全部(93%左右)下降,都发生在1945年之前。 [24]
不过,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占领时期的情况也极为重要,它将战时推行的各种措施永久化并使它们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对日本国民所做的新年文告中说的那样,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干预聚焦于征税、公司治理和劳动组织方面,此前在所有这些领域,战争的领导者已经对原来的那些财富精英造成了巨大的财务痛苦。由此,战争以及紧接着的战后岁月,促成了这样一次长久性的转变:一个富有且强大的、既控制着管理又索要高额股息的股票持有者阶级,转向一种实施终身雇佣、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的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公司系统。除土地改革以及商业和劳动关系重构之外,累进性的征税也是维系战时矫正的关键机制之一。20世纪50年代税收规范化之后,日本税收系统施加于顶层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达到60%~75%,对最富有者征收的财产税税率超过70%。正如对承租者的保护抑制了房产租金收入,以及集体谈判确保了持续的工资压缩一样,这些措施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还在遏制收入不平等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作用。 [25]
战争及其后果使得矫正过程不仅突如其来、规模巨大,而且经久持续。这段日本历史中最血腥的岁月,这场夺走了几百万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的战争,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平等化结果。一种新型的、要求大规模地理和经济动员的战争类型,使得这一结果成为可能。极端的暴力已经在日本社会中矫正了极端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这一从全民动员到毁灭和被占领的冷酷进程中,全面战争引发了全面矫正。
[1]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33–136 table 3A.2 (income shares); 148 table 3B.1 (estates); 81 fig.3.2 (Ginis), with Milanovic 2016: 85 fig.2.18.
[2] “向丹麦看齐”代表了一种学术上的简单说法,意指一个国家建立了高度有助于提升人的福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概念可追溯到Pritchett and Woolock 2002 :4,其流行尤其得益于Fukuyama 2011: 14。
[3] Saito 2015: 410; Bassino, Fukao and Takashima 2014: 13; Hayami 2004: 16–17, 29–30.
[4] 根据最近的数据,该国的基尼系数在1850年时为0.35(这当然是一个推测值),1909年时上升到0.43,接着1925年、1935年和1940年时,又分别升至0.5、0.52和0.55:Bassino, Fukao and Takashima 2014: 20.表5。有关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情况,参见第19页表1。它们表明学界对不平等在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变动趋势缺乏共识,不平等程度在这一时期不是持续上升,就是先上升后下降。也可参见Saito 2015: 413–414有关后幕府时期不平等程度有可能逐渐加剧的论述。WWID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前1/3的时间里,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虽然也出现过短期的波动,但总体上是相当稳定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sequalization: Nakamura and Odaka 2003b: 9, 12–13, 24–42; Hashimoto 2003: 193–194; Saito 2015: 413 n.57;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0.
[5] Nakamura 2003: 70 table 2.5, 82.
[6] See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0–102 for this trio.For the various state interventions, see esp.Hara 2003 and Nakamura 2003; and cf.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1 for a very brief overview.Controls: Nakamura 2003: 63–66 table 2.2.
[7] Nakamura 2003: 85; Okazaki 1993: 187–189, 195.
[8] Takigawa 1972: 291–304; Yuen 1982: 159–173; Dore 1984: 112–114; Kawagoe 1999: 11–26.
[9] Kasza 2002: 422–428; Nakamura 2003: 85.Kasza 2002: 429指出:“就日本的社会福利状况在1937—1945年间发生的转变来说,战争所起到的作用盖过了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10]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1; 129–130 table 3A.1.
[11] Capital stock: Minami 1998: 52;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86;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2.Losses: Nakamura 2003: 84;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86.Bombing: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1946: 17.
[12] Capital income share: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91 table 4.4; Moriguchi and Saez 2010:139 table 3A.3, and see also 91 fig.3.7.1886—1937年,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平均而言大约是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一半。Income shares: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88 fig.3.4; 134–135 table 3A.2; WWID.
[13] GNP and exports: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87–88.
[14]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29–30 table 3A.1; cf.Nakamura 2003: 90–92.For large variation in rat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dices, see Kuroda 1993: 33–34; and cf.also Teranishi 1993a:68–69;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89.
[15] Nakamura 2003: 87; Miwa 2003: 335—336.
[01] 预想结果为防范军国主义。——译者注
[16] Miwa 2003: 339–341.1946—1950年间,实际GNP确实增加了40%,特别是消费而非投资方面: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87。
[17] Miwa 2003: 347; Minami 1998: 52;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2; Nakamura 2003: 98 table 2.14; Teranishi 1993b: 171–172;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90.
[18] Nakamura 2003: 87; Minami 1998: 52; Estevez-Abe 2008: 103; Miwa 2003: 345; Miyazaki and Itô 2003: 315–316; Yonekura 1993: 213–222.Quote: Miwa 2003: 349.
[19] Miwa 2003: 336–337, 341–345; Nakamura 2003: 86–87, 91 (quote).这一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措施的目标被表述为“清除战时的收益”( Miwa 2003: 346)。从所观察到的收入缩减的真实情况来看,这一点更多是想当然的,而非真实发生了的。
[20] Yamamoto 2003: 240; Miyazaki and Itô 2003: 309–312.
[21] Teranishi 1993b, esp.172;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38 table 3A.3.
[22] Unionization: Hara 2003: 261; Nakamura 2003: 88; Miwa 2003: 347; Yonekura 1993: 223–230, esp.225 table 9.3; Nakamura 2003: 88; cf.Minami 1998: 52.Benefits: Hara 2003: 285;Yonekura 1993: 227–228; Estevez-Abe 2008: 103–111.
[23] Memo: Miwa 2003: 341; and see also Dore 1984: 115–12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ancy, rural poverty, and aggression.Land reform: Kawagoe 1999: 1–2, 8–9, 27–34;Takigawa 1972: 290–291; Yoshikawa and Okazaki 1993: 90; Ward 1990: 103–104; and see also Dore 1984: 129–198 and Kawagoe 1993.MacArthur: in a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Yoshida Shigeru from October 21, 1949, quoted by Ward 1990: 98; Kawagoe 1999: 1.
[24]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94 table 3.3.
[25] Okazaki 1993: 180;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04–105.For the MacArthur quote also used in the section heading,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1946: 135.
日本的经验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战”,或者更广泛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类似的结果吗?答案很简单,是的。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因特定的环境构成而有所不同,但夏尔·戴高乐所谓的1914—1945年间“三十年战争的戏剧”,导致了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巨大且显著的分散化。虽然这其中还包含一些我在第12章和第13章论及的替代或补充性因素,但毫无疑问,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及其经济、政治、社会、财政方面的因素与后果,是最强有力的矫正手段。 [1]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期间急剧下降,并在战后维持着较低的水平。参与了这场战争且存有可比数据的其他几个国家,如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其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图5.1)。 [2]
对其他一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有关社会顶层收入份额的证据资料,时间可分辨性更差,故而会掩盖掉战时紧缩发生的突然性。尽管如此,隐含的趋势是相同的,就像德国和英国最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图5.2)。
两件相关联的事情最为重要:交战当时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如图5.2中德国的情况所示,战争刚结束时的相应数据资料是不可得的),以及战争在战后数十年中产生的长期影响。我将分几个阶段来分析它们。首先,我会就那些已公开发布了相关证据的国家,分析其顶层收入份额在战时的演变情况,指出它们是如何随各国卷入冲突的程度深浅而不同的。其次,我会对战时的矫正与后续的发展进行比较,以说明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所具有的特殊性。再次,我会对导致战时收入和财富分配压缩的多种因素做出评论——但是远没有对日本的分析那样深入细致。最后,我将论述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多大程度上应该为1945年之后物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持续且通常是不断强化的平等主义趋势负责。

图5.1 4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935—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表5.1归纳总结了当前已发布的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发展变动情况的信息——一般是有关顶层1%群体的信息,但也有少部分反映的是人口占比更小的社会阶层的信息,如顶层0.1%甚至0.01%群体的收入信息,因为只有聚焦这些更小的阶层,才能够保证信息必要的时间深度和准确度。时间基准是以1913—1918年来代表“一战”,以1938—1945年来代表“二战”,某些也采用了时间上稍有不同的数据,并且这些时间区间与各国参战时间并不严格吻合。请注意:所有这些数据都不应被看成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些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终归是我们能掌握的最好的数据。它们在时间上比标准化基尼系数追溯得更远,能够使我们很好地体会到在收入分配的最顶层曾发生过怎样强烈的变化。也即是说,尽管我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会造成量化精确的印象,但这个表格不应使我们误以为可依据其表面数值接受其中的所有细节。这些证据所能做的,是传递一种有关变化方向和幅度的感觉,这是我们最多能指望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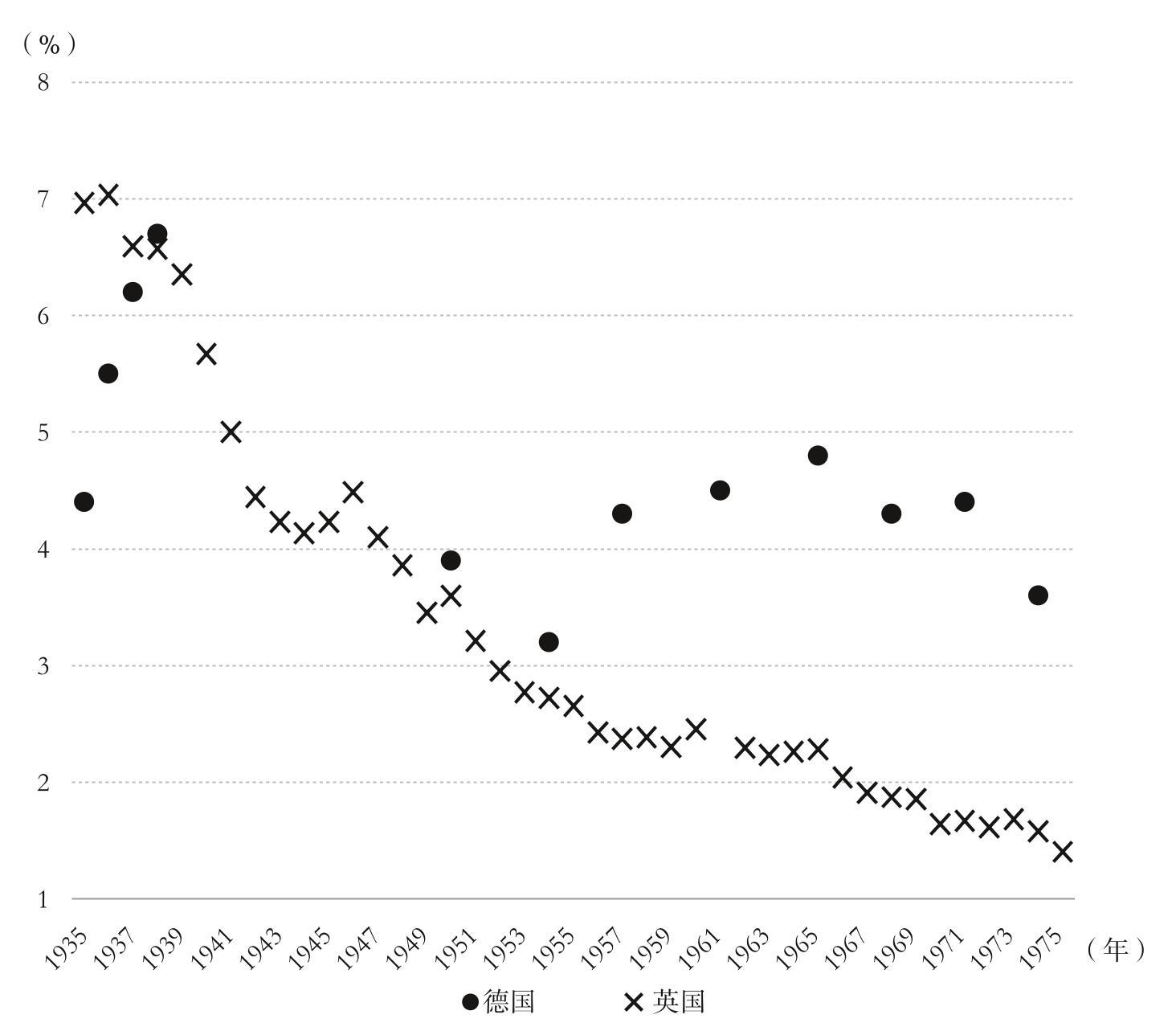
图5.2 德国和英国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以百分数表示)
表5.1 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发展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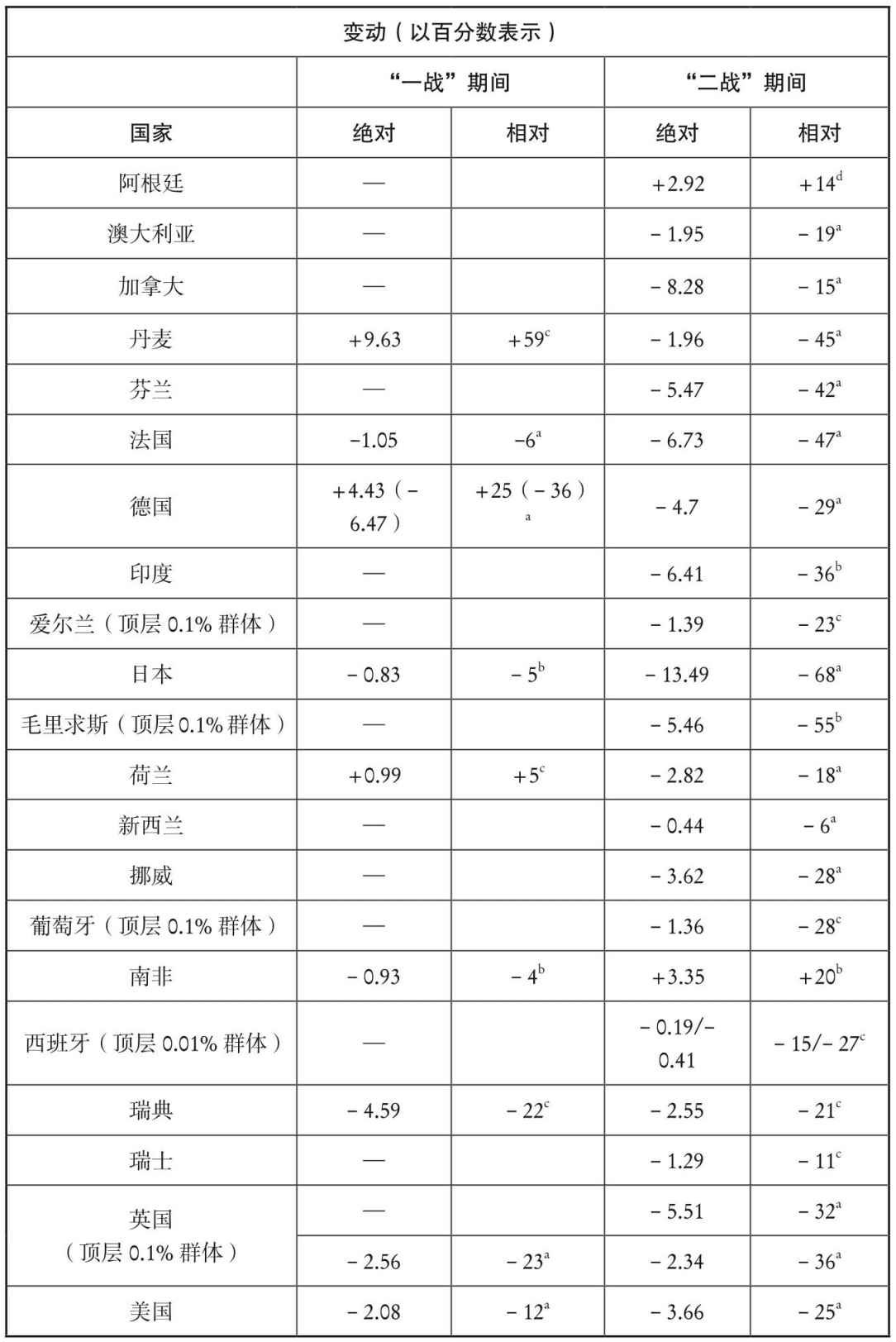
注:除非有特殊说明,表中数据皆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右上标a指主要参战国,b指次要参战国及殖民国,c指旁观国,d指中立国。
这一列表反映出“二战”时期的数据有着更高的质量,从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的趋势。在那些积极参战的先锋国家(通常也是被占领的国家),顶层收入份额相对于战前下降的平均百分数达到31%,鉴于该样本包含了12个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力的发现。(若撇开新西兰这个多少是边缘性的个案,平均下降幅度会被抬高到33%。)中值下降率介于28%~29%之间,并且每一个个案都显示出一种净下降趋势。表中还包含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程度更低或者更偏远的殖民参战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南非),但从中并未观察到一致的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达到了24%。中立性邻国的样本同样较小(冰岛、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但至少体现出一种一致的负向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也达到24%。阿根廷,这个几乎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中立且地理上与主战场相距甚远的国家,显然是个例外: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比战前提高了14%。
“一战”时期的证据资料不仅更少而且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反映的是,与“二战”相比,“一战”在对不平等产生影响的时间方面的不同。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在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在法国,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这些影响延迟至1918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因此,“一战”对主要参战国的总体影响结果,取决于我们对德国采用的是1918年还是1925年的数据:只有在采用后者时我们才能观察到顶层收入份额19%的平均下降幅度。两个边缘化的参战国显示了5%的平均下降率,三个中立邻国经历了14%的上升,但未发现一致的趋势。据此,我们暂且可以得出结论:“二战”对精英阶层的收入产生了极其有力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还波及未参战的邻国。该时期仅有的两个经历了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国家,是距离战争最远的国家。
现在,我们必须把战时发生的这些变化,与在“二战”结束后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出现的新进展联系起来。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积极参与冲突的国家的顶层收入份额都在继续下降,有的是持续不断地下降,有的则是在战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恢复后继续下降。总的来看,这一趋势持续了几十年,但情况最终在1978—1999年间的不同时间点开始逆转,顶层的市场收入份额重新开始上升。表5.2比较了各国的顶层收入份额(除特别标明外,皆指顶层1%群体)在战时和战后,以及部分国家(当变化迅速时)在大萧条时期以百分数表示的年平均缩减率。当数据可得时,战后时期的下降率是以两种方法计算的:(1)计算从“二战”结束时到随后顶层群体收入份额达到最低值年份之间的净下降率,不考虑其间的波动情况;(2)计算顶层收入份额从战后最高值到最低值之间的连续下降率,考虑其随时间变动的情况。表5.2中“战时下降率相当于战后下降率的倍数”一栏,粗略测度了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战时年下降率相对于战后年下降率的倍数。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模式。不管以何种方法计算战后的下降率,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的年下降率总是比它高出几倍,甚至常常是好几倍。对许多主要参战国来说,规模上的差别是巨大的。在法国,顶层收入份额战时的下降速度是接下来38年下降速度的68倍:在1938年之后该国顶层收入份额出现的所有缩减中,有92%发生在1945年以前。这个比例在加拿大几乎一样高,其1938年后发生的全部缩减中有77%出现在战争期间。日本的情形独一无二:其大战期间发生的矫正是如此剧烈,以至1945年是创下顶层收入份额最低历史纪录的年份,该纪录此后再也没有重现。在英国,其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大战之前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缩减,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两次大战期间的年下降率较战后的情况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芬兰在“二战”时期的情况同样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些受战争影响更小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和印度,战时的缩减率仅是战后缩减率的3~5倍。(英国在“二战”时期的下降率虽然比较温和,但其在“一战”时期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减。)
德国的证据更为复杂。假如我们把对“一战”时期的测算时间定在1925年,亦即1919年后首个留有确切数据信息的年份,从而把延迟的矫正效应考虑在内,那么,德国“战时”缩减率就比后“二战”时期的缩减率高出一个数量级。另一个问题是,因为缺少1938—1950年的数据,所以不能判断1938—1945年这一阶段发生了多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工业化国家来说,“二战”产生了十分强劲的矫正效应,其影响远大于此后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很难用别的方式来强调从战争到和平时期收入不平等演变的不连续性了。相比而言,有关“一战”时期的信息不仅更少,而且更难解释。在后面考察各国情况时,我会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与战争有关的矫正存在时滞问题这一观察到的差异。
表5.2 各国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下降率的逐期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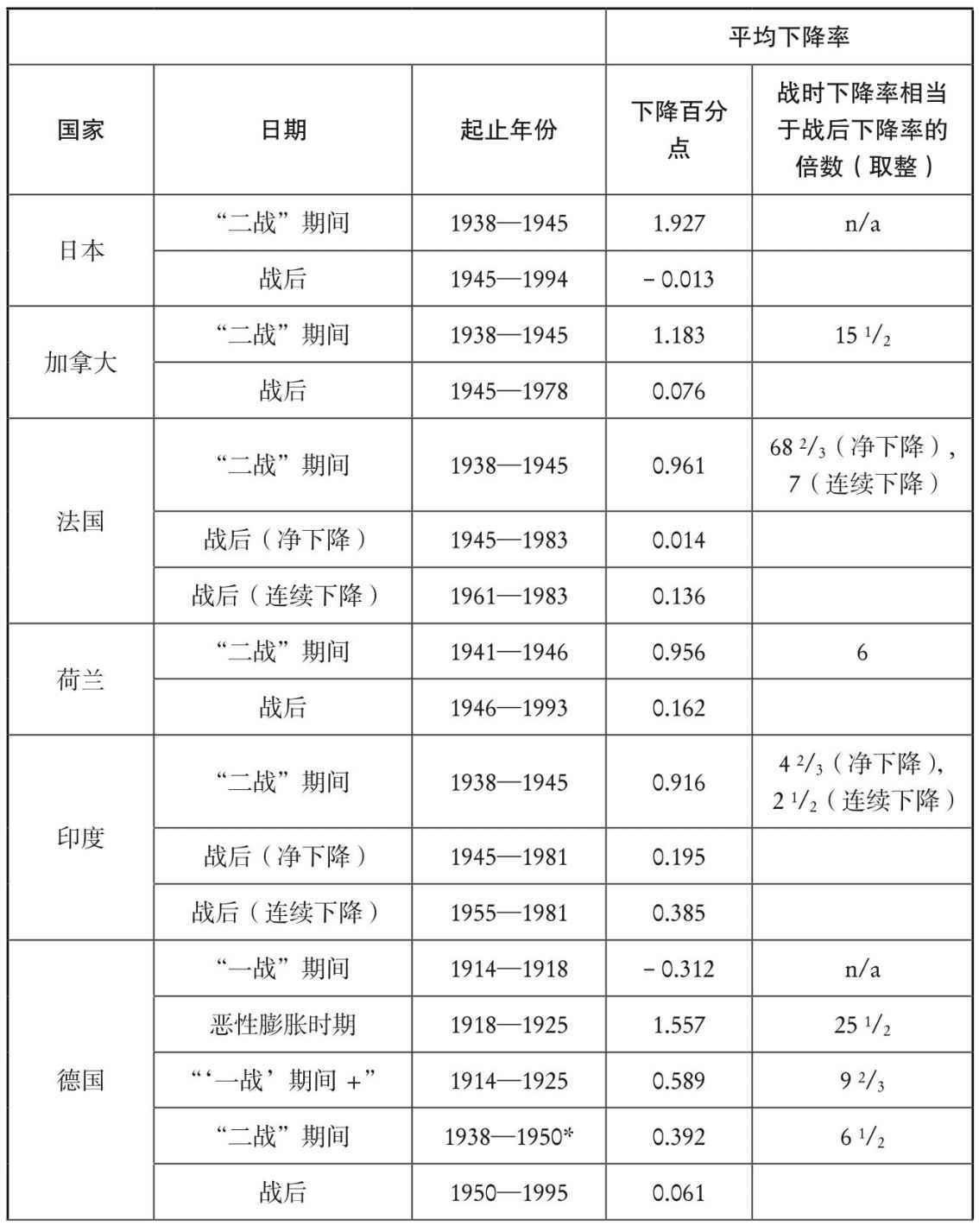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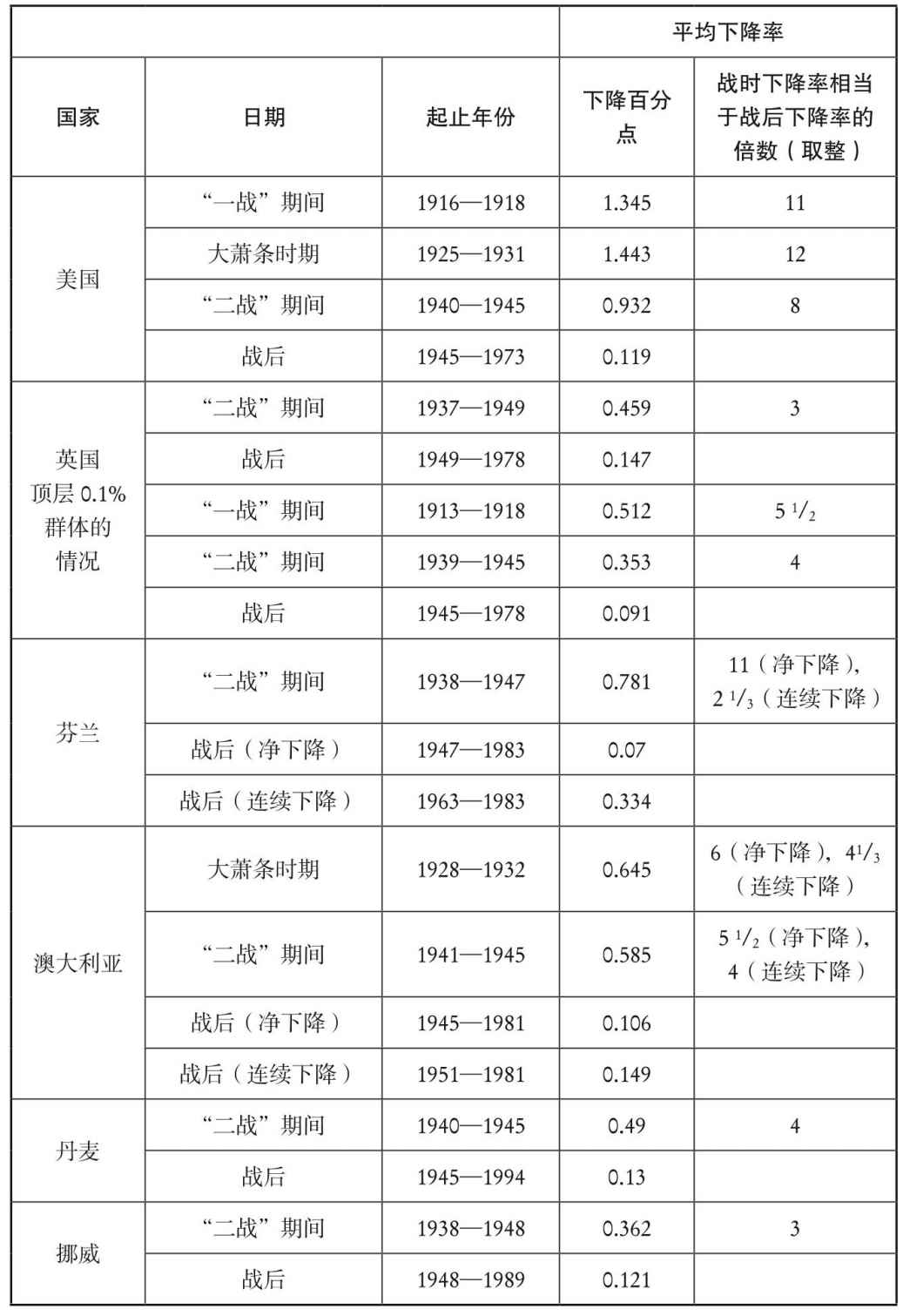
有关国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信息,虽然可获得的难度比顶层收入份额信息更高,但同样显示出了在战争时期的非连续性。由此可推知,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所有净下降,都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按照一种测算方法,其基尼系数在1931—1939年出现3%的温和下降之后,在随后的6年里又暴跌了整整10个百分点,接着直至1980年都一直稳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按照另一种测算方法,它在1929—1941年间降低了5个点,战争期间又降了7个点。英国的税后收入不平等在1938—1949年下降了7个点(1913—1949年的下降幅度大概是它的两倍)并随后趋于平缓直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证据较少,但它们表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甚至出现了更陡峭的下降,降幅至少达到了15%,并接着趋于稳定直到1980年左右或者更晚。 [4]
财富集中方面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力。在证据可得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最高纪录恰好发生在“一战”爆发之前。1914—1945年间,出现了顶层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图5.3)。 [5]
在卷入了一次或两次世界大战、有可用数据的7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平均减少了17.1个百分点(相当于记录在册的国民私有财富总量的1/6),相对于“一战”前的平均峰值48.5%,大约下降了1/3。比较发现,在最早报道出来的战后值与总体最低纪录值(它们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00年之间的不同时期)之间,相差了13.5个百分点。这看起来似乎使得战后发生的缩减在规模上可与战争时期相比,但我们必须记住,后者不仅包括了两次大战之间各年份,常常还包括了1945年之后几年发生的缩减,这意味着很难按年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此外,若考虑到财富的分散化是靠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在征收的累进性遗产税来维系的,此过程本来该持续更长的时间,这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我后面要表明的,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税收本身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另外,这些国家中的5个,其顶层财富收入份额在战争时期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所出现的下降,占其总下降量的比重介于61%~70%之间。第6个国家,即英国,这一时期的下降实际上非常大(超过国民私有财富量的1/5)。考虑到该国1914年以前的财富集中度已经非常之高,其战后必须出现甚至更剧烈的下降,才能使顶层财富份额处于普遍具有的20%左右的新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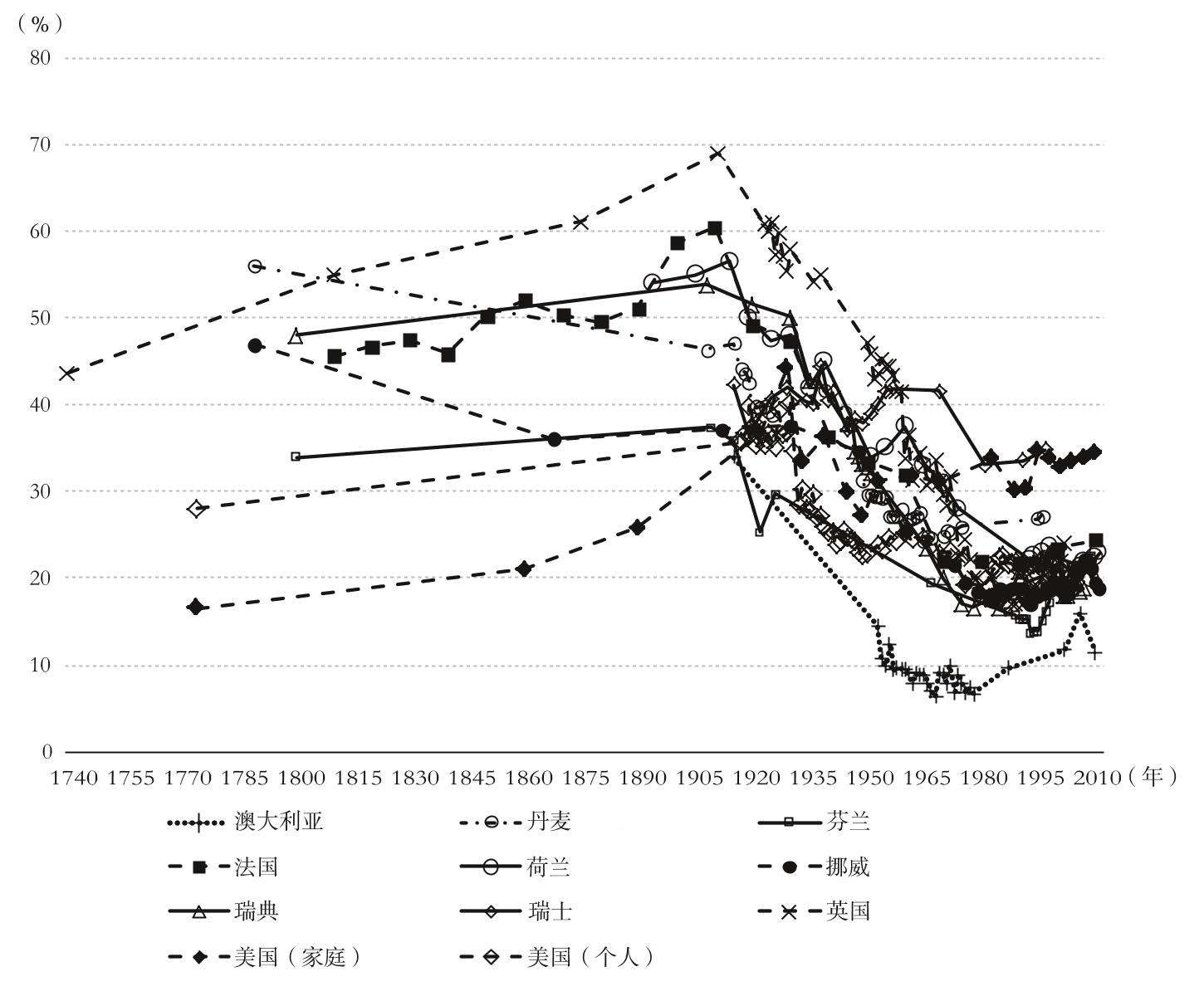
图5.3 10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1740—2011年(以百分数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最顶层的财富缩减与“1%”顶层群体的财富缩减相比,可能更为显著。举一个特别令人震撼的例子,法国最富有的0.01%群体的财产,其价值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降了3/4以上,“二战”期间又下降了2/3。这意味着两次大战总共缩减了近90%,而其顶层1%群体财富份额的缩减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所有这些的关键之处当然在于,时间拐点恰好出现在世界大战开打之时,财富分配普遍朝着更大不平等方向发展的早期趋势受到抑制并被有力逆转。我们也不要忘了,如果不发生激进的征用和再分配,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以近乎重构收入份额那样快的速度来重构财富份额。 [6]
战争期间精英阶层的大量财富不仅被用于再分配而且事实上被抹掉这一点,从三个主要参战国私人财富的国民收入占比变化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图5.4)。最剧烈的下降出现在“一战”时期,紧接着是“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前后的再一次下降。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映,资本收入在最高收入家庭所得中的份额直线下降(图5.5)。这些观察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阶层的损失首先是一个关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现象。为什么战争对资本所有者如此不利呢? [7]

图5.4 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全世界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1870—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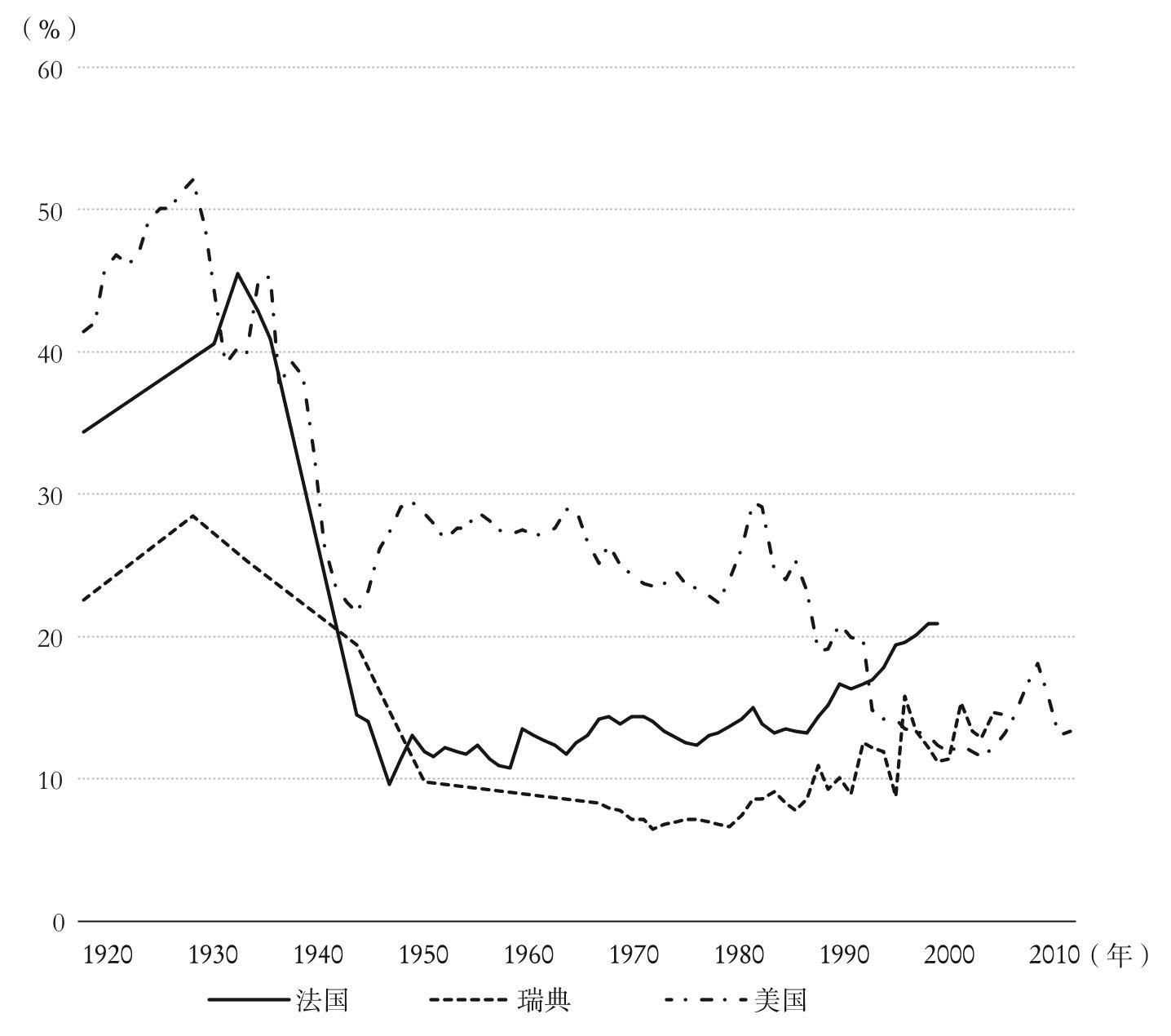
图5.5 法国、瑞典和美国顶层1%群体的资本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1920—2010年(以百分数表示)
两次世界大战不同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所有其他冲突。人力动员和工业生产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战”大概动用了近7000万的士兵,这是一个在战时各年份未曾被超越的数字。战死的士兵接近900万或1000万人,此外有700万左右的平民丧命于战争或相关的苦难。法国和德国动用了其全部男性人口中的40%,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动用了30%,英国、俄国、美国分别动用了25%、15%、10%。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强行用于支持战争。就我们掌握了相关信息的那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无论在何地,国家征用的GDP份额都增长了4~8倍(图5.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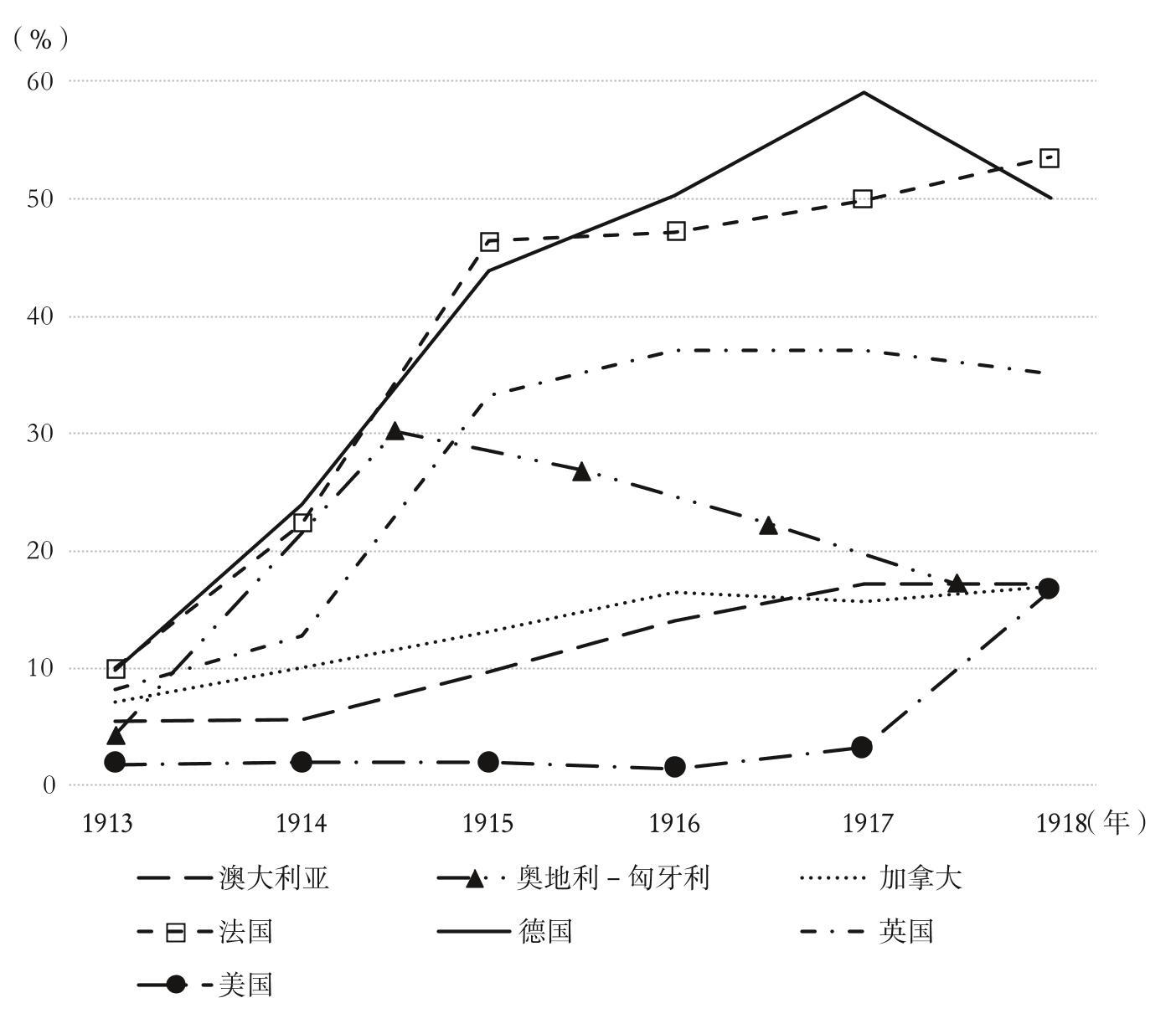
图5.6 7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13—1918年(以占GDP的百分数表示)
法国和德国都损失了大约55%的国民财富,英国损失了15%。“二战”的情况更糟。大约超过1亿的士兵被动员,战死的超过2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的平民罹难。主要参战国制造了286000辆坦克,557000架战斗机,11000艘海军舰艇,超过4000万支步枪,以及许多其他武器。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战争的成本和损失总额(包括生命损失)据估计达到4万亿美元,比大战爆发时全球GDP高出一个数量级。在征服欲的驱使下,国家占有GDP的份额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43年,德国大概有73%的GNP由国家支配,几乎全部用于支持战争,挤出来的一部分用于被征服的人口。按一种方法测算,日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同样靠榨取其将死帝国的资源,挥霍掉了多达87%的GDP。 [9]
这些耗资巨大的争斗大部分是靠借款、印钞票和课税来维持的。借款以不同方式被转嫁成未来为偿付公债而征的税收,或借助通货膨胀而逐渐消失,抑或拖欠违约。只有几个西方大国成功地管住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和英国,价格从1913—1950年只上涨了3倍。其他交战国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期价格在法国上涨100倍,德国上涨300倍,日本单是从1929—1950年价格就上涨了200倍。债券持有者和出租人被淘汰出局。 [10]
直到1914年,如果说存在所得税的话,那么收入边际税率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很低的。高税率和急剧累进性的征收是战争的产物。最高税率在“一战”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激增,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回落,但从未彻底回落到战前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通常是出于应付大萧条的余波,税率再次上涨,并在“二战”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大概从那之后它们一直保持着缓慢下降的态势(图5.7)。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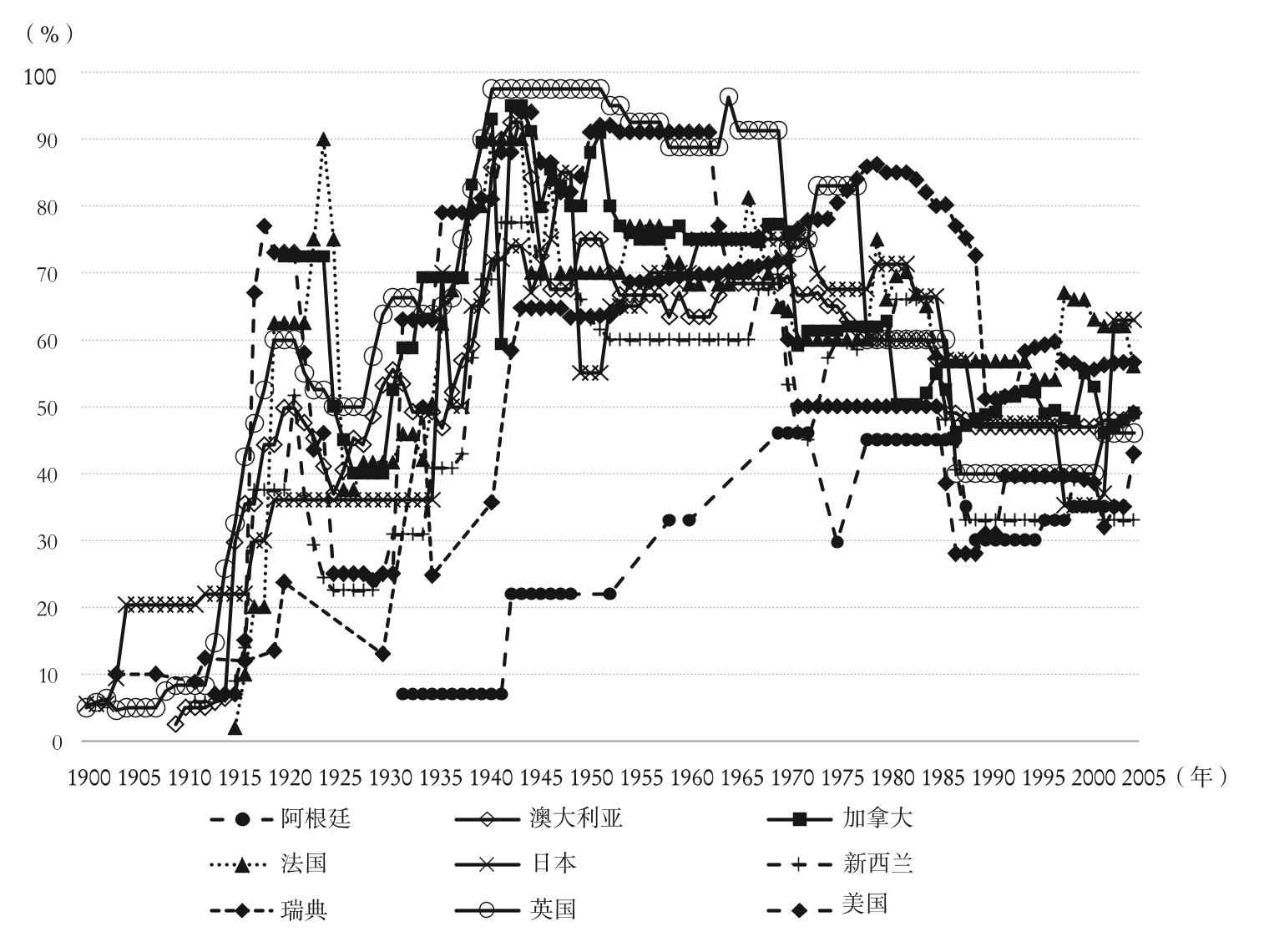
图5.7 9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1900—2006年(以百分数表示)
通过对不同国家出现的这些发展变化做出平均化的处理,潜在的趋势得以显现,同时还凸显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影响财政政策演变之关键枢纽的极端重要性(图5.8)。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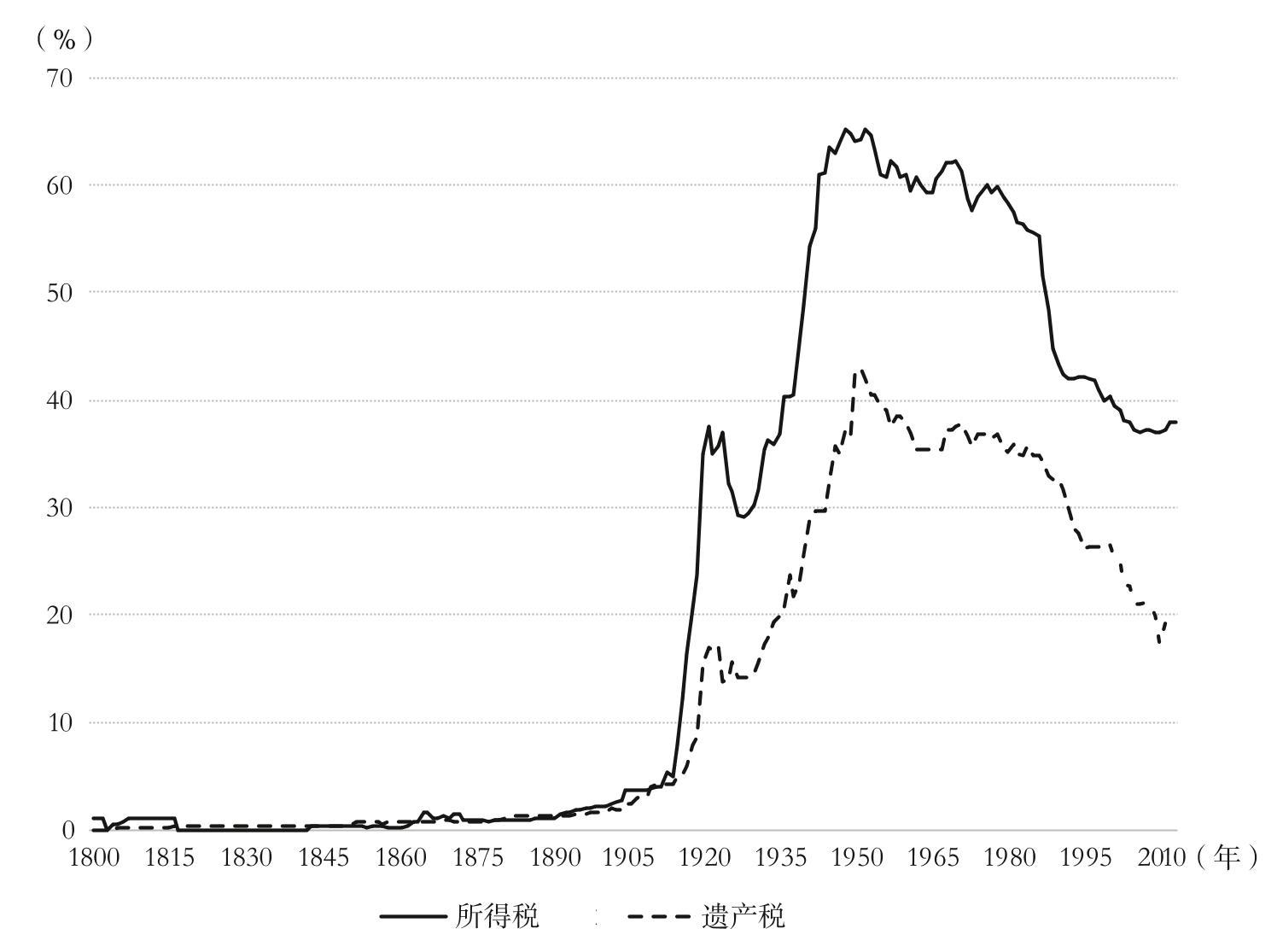
图5.8 20个国家平均最高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1800—2013年(以百分数表示)
图5.8清楚地表明了战争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它在1904—1905年为满足俄日战争的需要就已经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顶层所得税率,而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对“一战”的一次预演。作为非参战国的瑞典,最高税率在“一战”时期很大程度上没有出现激增,并且直到下一次战争时都低于其他国家。最令人惊讶的是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阿根廷,它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发现,在参战国中存在一种很强的财政–战争效应,但在其样本中的其他国家,这种效应要弱得多(图5.9)。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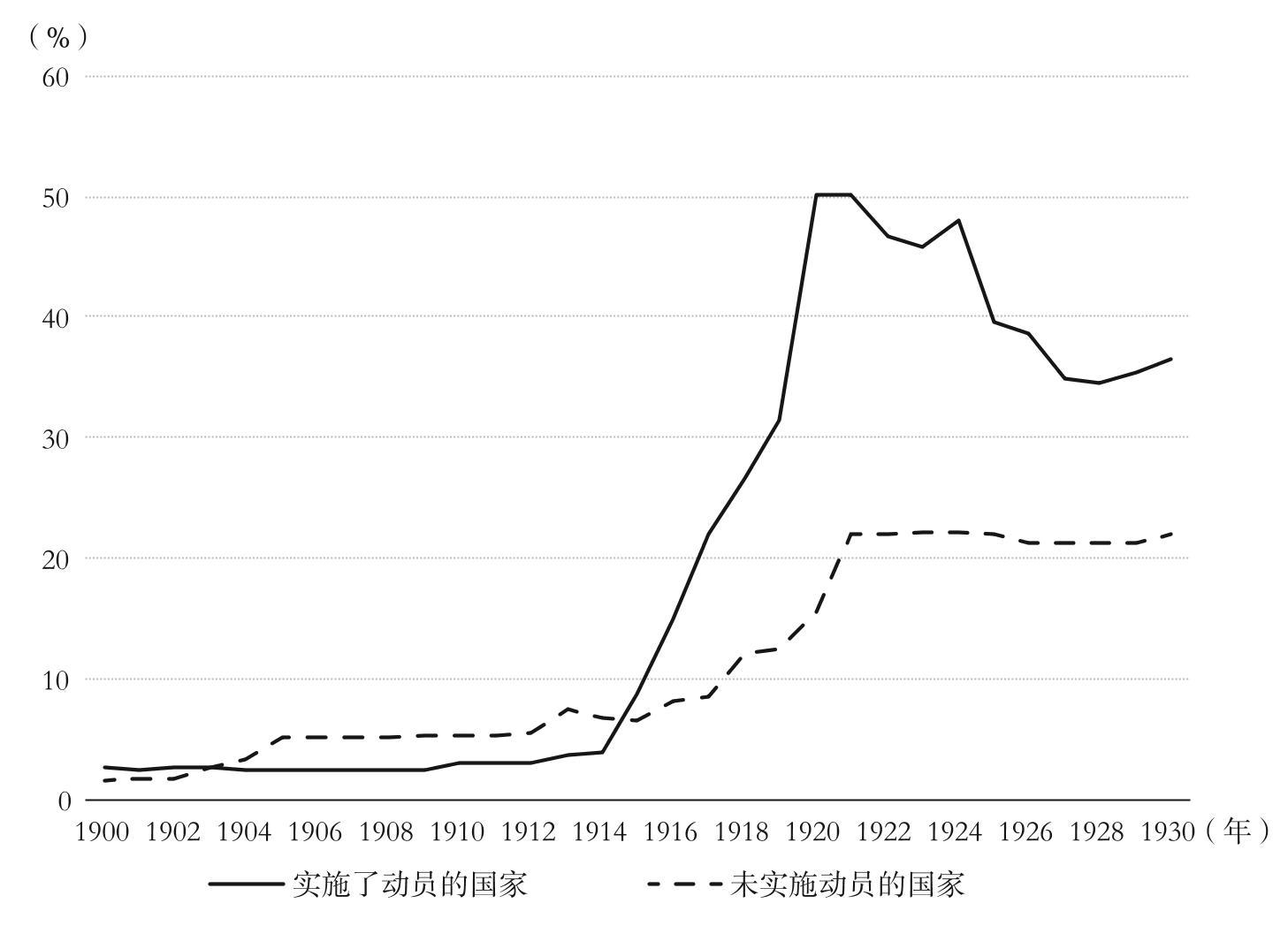
图5.9 “一战”与17个国家的平均最高所得税率(以百分数表示)
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税率上的累进分级,以及瞄准收入顶层的财富精英,构成了财政矫正的三大主要要素。舍韦和斯塔萨维奇论证指出,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在征税策略方面之所以不同,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高,而且更是因为它们需要更高程度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能够转化为从富人那里不成比例地狠狠抽取资源的政治压力。考虑到基于年龄或特权以及不愿放弃从战争产业中谋利的机会等方面的原因,财富精英服兵役的可能性更小,大规模征兵本身并不是一种平等化力量。对公平的关注要求在实施作为一种实物税的军事征兵的同时,征收英国工党在1918年宣言中所说的“富人兵役税”。尤为重要的是对战争利润的征税:“一战”时期,英国施加于被认定为“额外”利润之上的最高税率达到63%,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则达到80%。1940年,罗斯福总统要求采取类似的措施“使少数人不能从多数人的牺牲中获利”。战争时期对公平的重视还为针对非劳动收入的沉重负担提供了辩护:虽然累进性的所得税是用来压缩不平等的专门手段,但真正对富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强有力影响的是财产税。 [14]
公平考量带来的矫正效应显著地受到了统治类型的影响。“一战”时期,英国、加拿大、美国等民主国家都试图“敲富人的竹杠”,而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这类更专制的政体更偏向于通过借债或印钞票来维持战斗力。然而,后者后来以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革命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类震荡同样起到了缩小不平等的作用。特别是“一战”期间,在一种支撑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通用融资模式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所使用的矫正机制是非常不同的。 [15]
法国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受了最严重打击的国家之一,它先是在整个“一战”中饱受战火的摧残,尔后又在“二战”中两次遭到入侵和占领。在第一次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损失了1/3的资本存量,资本收入在国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1/3,同时GDP同比缩减。税收提升得很慢:战争开始时最高遗产税率仅为微不足道的5%,并且,尽管在1915年首次引入了一项所得税,但其有效的最高税率在余下的战争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低水平,直到1919年才显著提升。与财产税的增长一样,创设于1916年的战争利润税也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产生大的收益。这一滞后效应,连同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起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而非战争当时的一个现象,战争利润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应。截至那个10年的中期,规模最大的0.01%财产的平均价值,与战前水平相比,已缩水3/4以上。 [16]
“二战”时期法国遭受了德国长达4年的掠夺性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行动也造成了大量破坏,故而其精英阶层的财富继续缩减。这一次,2/3的资本存量消失殆尽,损耗率是“一战”时期的两倍。曾经占法国最大额财富1/4的外国资产荡然无存。顶层收入份额在此期间急剧下降,战后通货膨胀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债券和战争债务的价值大幅缩减。如皮凯蒂所说,由于资本轮番地遭到了战争、破产、租金控制、国有化和通货膨胀的摧残,所以1914—1945年间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完全源于非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两次大战累积形成了巨大的矫正效应:10000%的通货膨胀率掏空了债券持有人,实际租金在1913—1950年间下降了90%,1945年实施的一项国有化计划以及针对资本所得征收的一次性总付税(针对大额财富以及战争期间大幅增值的财富的税率分别达到20%和100%)使得资本积累几近于零。最顶端0.01%群体的资产价值最终在1914—1945年间下降超过90%。 [17]
在英国,最高所得税率“一战”期间从6%提高到30%,同时,就财政收入而言,针对公司征收的一项新的战争利润税(1917年时税率已提升至80%)成为最重要的税种。该国在这次大战中损失了14.9%的国民财富,“二战”期间又损失了18.6%。进入顶层0.1%群体的收入门槛线,“一战”时从平均收入的40倍下降到30倍,“二战”时又从30倍下降到20倍。顶层税后收入份额的下降(从1937年起才有报道)甚至更为显著——1937—1949年间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近一半,最顶端0.1%群体的份额则下降2/3。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占私人总财富的份额从70%缩减到50%——减幅虽不如同期法国从60%降至30%那般巨大,但仍很显著。 [18]
美国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经历则表明,由战争引起的大幅度矫正在没有物质破坏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该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发生在三个独立的时间区间,即:“一战”期间下降了1/4,大萧条时期再降1/4,“二战”时期在既有基础上又降30%。总体来看,1916—1945年间,顶层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的下降约为40%。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趋势在更高的收入层级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同期,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降幅高达80%。对收入份额的分解显示,其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收益下降驱动的。顶层的财富份额在大萧条时期的下降幅度甚于“二战”时期的下降幅度,但累积起来比大萧条前的峰值水平低了1/3。与其他主要参战国的情况相比,大萧条在矫正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大于战争本身:我会在第12章回到这一点上。 [19]
尽管如此,战时的矫正效应仍然非同小可,出于战争融资的目的而征收的、急剧累进的税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1917年的《战争税收法案》将附加税最高税率从13%提高到50%,并对高出投入资本金9%部分的利润征收20%~60%的税。由于战争支出继续增长,1918年战争刚刚结束时通过的税收法案,又对最高收入和超额利润施加了甚至更高的税率。针对50000和100000美元收入的有效税率,分别从1913年和1915年的1.5%和2.5%上升到1918年的22%和35%。1916年新创资产税,其最高税率在随后一年从10%上升到25%。战争是推行这些积极干预政策的唯一原因:“为‘一战’做动员的高度不确定的政治局面,促成了民主–国家主义税收体制的诞生。”虽然1921年和1924年的税收法案废除了超额利润税,并大幅降低了附加税税率,但保留下来的最高税率依然远高于战前的水平,且最为紧要的是,资产税依然如故。由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战后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最高收入的再度飙升,另一方面发现在顶层的收入份额和政府声称所拥有的财富之间存在某种棘轮效应,即便是在日益变大的财政漏洞使得累进税制面临被掏空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20]
随后出现的均等化局面,部分要归因于加在收入和继承性财富之上的高边际税率。这一过程开始于新政,并在随后的战争期间进一步得到发展,直至达到顶峰。如罗斯福所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面临巨大危险、所有额外收入都应该被用于打赢战争的时代”,所得税和资产税的最高税率分别在1944年和1941年时达到了94%和77%的峰值,并且,最高税率适用的收入门槛大幅降低,以至作为重税对象的高收入群体进一步扩大。超额利润税也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抵制本该以累退方式征收的联邦销售税——考虑到当时即便是瑞典也有该税种,这的确称得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限制条件。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施行了工资控制政策,其结果是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领域更为广泛地缩减。由于有责任确保所有工资收入都符合1942年冬颁布的维持工资稳定的法案,该机构当时只准备在低收入群体(不在高收入群体)中提高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高收入群体在总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与低收入者相比,那些工资水平最高的人损失最为惨重:1940—1945年,在工资分布中处于顶端90%~95%的领薪者,工资份额下降了1/6,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1/4,那些顶层0.01%群体的下降幅度更是高达40%。企业做出的反应是提供津补贴而不是涨工资,这本身也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提高了。国家干预及其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总体工资收入结构遭到压缩,而这意味着在“‘二战’所特有的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趋势。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断强化着这一趋势。与更低层次工资收入者的情况相比,高管津贴在1940年之后不断下跌,而在此前的大萧条时期它曾一度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水平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工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和公司规模报酬的持续下降。由于这些相互一致的变化,收入基尼系数在战争期间快速下降了7%~10%,与此同时,多项指标显示,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和工资水平在相同的年份里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们一直未发生进一步的变动。 [21]
加拿大的情况则多少有些不同,具体说来,大萧条并未对其顶层收入份额造成明显的影响,但“二战”期间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分散化。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上升促成了这一变化:税率在1943年达到95%的峰值;加在前1%的工薪族身上的有效税率,1938年时仅为3%,5年后一下子就升到48%。 [22]
德国顶层收入份额的演变情况多少有些异常,因为在军事动员率和国家支出都非常高的“一战”期间(图5.10),它们反而有所上升。 [23]
未发生大规模战时破坏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由于威权政府力图保护那些大发战争财的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有着亲密关系的产业部门中的财富精英,所以不平等程度出现了短暂的飙升。劳工组织被迫就范,与此同时,虽说引入了新的资本税,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类似于法国的。受战争暴利和低税收的双重影响,后者的顶层群体收入在1916年和1917年间一度趋高。德国政府维持战争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累进征税,其战争支出的首要来源是借债。虽然大约有15%的战争开支源于增发货币,但在严厉的价格管制之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尽管货币基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5倍,但以批发价格和食品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只达到了可控制的43%和129%。这与德国其他盟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匈帝国以消费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500%,伊斯坦布尔同期的消费价格上涨了2100%。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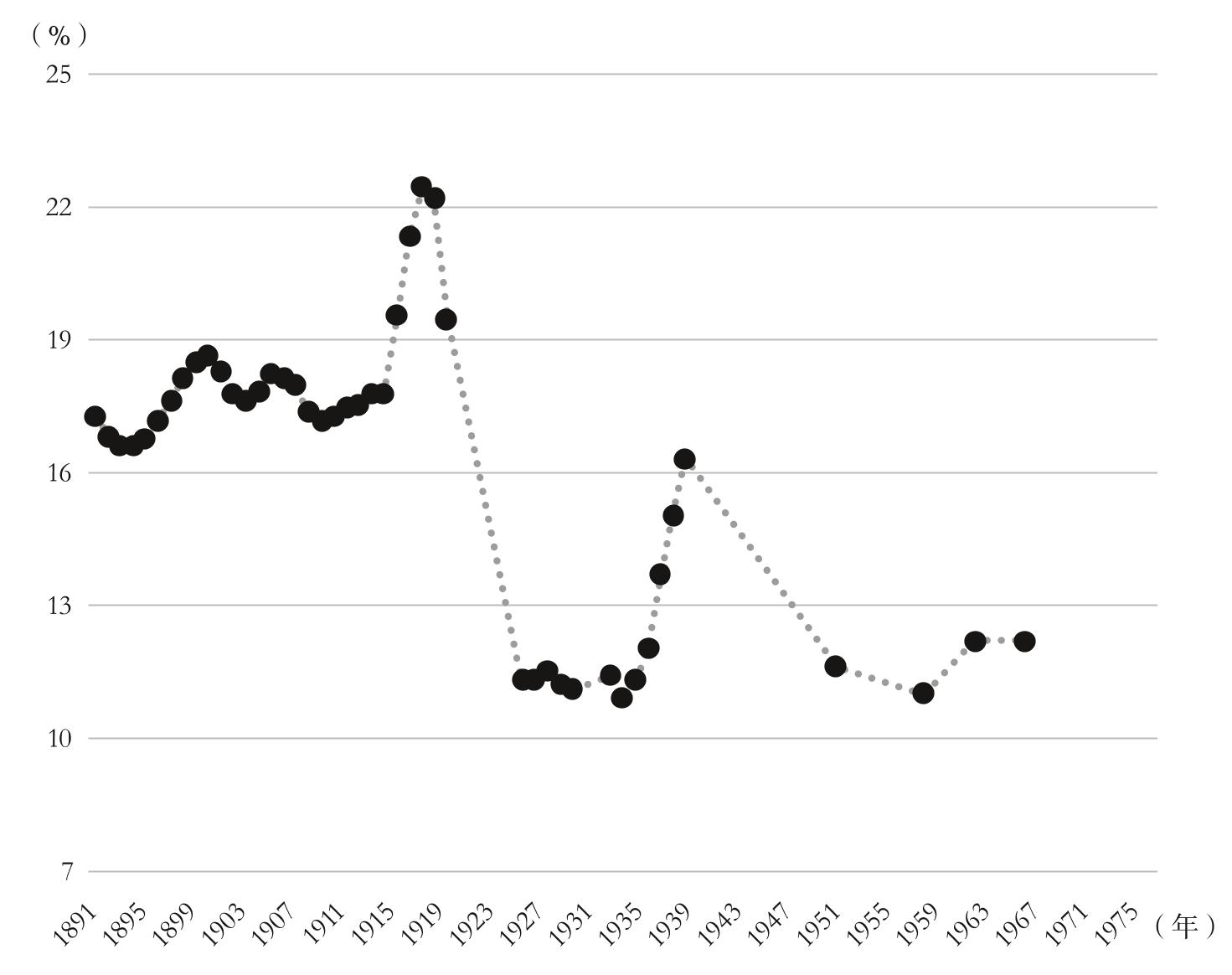
图5.10 德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891—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然而,战争的矫正效应只可能延迟,不可能避免。战后几年中出现的政治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发的局面,使得顶层群体收入大幅下跌:顶层1%群体的收入下降了40%,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更是出现了降幅高达3/4的塌陷式下滑。这些最顶层精英的遭遇,并未发生在那些处于收入阶梯第90~95百分位之间的人身上,与此同时,中产家庭的收入份额有所上升。政府实施的货币扩张政策,先是为了支持战争,后来则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以及实施社会和就业计划,其中,后者是1918年革命的直接结果,这场革命本身又源于战争。随着1919年和1920年时解除了对价格的控制,此前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一路狂飙。1914年夏季到1920年1月,依据柏林一户四口之家的消费情况计算的价格指数仅为1~7.7,但等到1923年冬季时,该指数已飙升至5万亿。放贷取息者的损失最大:即便是在企业主的收入份额得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仍然从15%降至3%。在这样一个总体财富大幅缩水的历史时期——1923年的实际国民收入比1913年时少了1/4~1/3,由于货币资产的分配更不平等,所以,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财富损失使得矫正效应进一步扩大。政策方面的变动也有助于这一平均化过程。战后几年,针对低收入劳工实施的工资调整政策带来了工资差距的缩小,1913—1925年,转移支付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两倍。最高遗产税率从0变为1919年时的35%也绝非偶然。 [25]
随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法规使得顶层的收入份额开始复苏,这主要得益于对消费和工资增长的限制,从新兴的军火工业中获利,以及对犹太人财产的征用。“二战”期间,德国夺走了法国、荷兰以及挪威30%~40%的GNP,从而缓解了其国内征税的压力。虽然缺少战争时期不平等的度量数据,但等到尘埃落定之后,顶层的收入份额已回落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水平。这不只是资本损失导致的结果,而是产出降低、财政改革以及通货膨胀联合作用的结果。因为盟军的轰炸主要集中于交通设施和民用住房,所以工业资产遭受的物质性损毁非常有限,1936—1945年,工业资本总量实际上增长了1/5。然而,工业净产出在1944—1950年下降了大约3/4。此外,该国还在战后三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6年最高遗产税率翻了两番,从15%升至60%。战时强迫性劳动导致的损失促成了劳动力的短缺,在此背景下工会得以重建,占领当局还施行了工资控制。同“一战”时的情形一样,在观察到的矫正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 [26]
在荷兰,顶层收入份额曾在“一战”早期因战争利润而出现过短时期的增长,但随后便急剧下降,直至战后1920—1923年的萧条时期结束,其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75%减至45%,净收入不平等大幅降低。大萧条时期,顶层收入份额再度下降,德国占领时期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亦是如此。“二战”给最高收入者带来的打击尤为严重,其中,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了40%。德国占领当局施行了工资控制——荷兰在获得解放后继续维持了这一措施,以及实行有利于最低收入阶层的政策;租金被冻结在1939年的水平上。战后,为补偿战争损失,曾一度保持在很低水平上的税率大幅飙升。 [27]
深陷“二战”之中的芬兰,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8—1947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依据应纳税的所得计算的基尼系数从0.46降至0.3。在丹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9—1945年下降了1/6,最顶层0.1%群体的降幅达到1/4,同时,20世纪30年代晚期—20世纪40年代晚期,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下降了1/4。被德国占领时期,丹麦政府大幅增税并对工资做出调整。这同与战争有关的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带来了与“一战”时期的情形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战”期间,虽然顶层的财富份额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故而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增加了。最后,在德国占领的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顶层收入份额同样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且下降速度远高于战后。1938—1948年,其顶层0.5%群体在总收入中丧失了近1/3的份额,同时顶层的财富份额也出现了下降。 [28]
上述概略式的调查表明,尽管具体的矫正途径在各国之间并不相同,但总体结果极为类似。低的储蓄率和受到抑制的资产价格,物质性破坏和外国资产损失,通货膨胀与累进性的征税,租金与物价控制,以及国有化等众多因素,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结果。这些因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解释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规模与时间变动情况。全面战争的压力,构成了它们共同的根源。皮凯蒂通过一般化其祖国(法国)的经验,大胆地提出:
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正是战争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震荡,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并不存在一种朝向更大平等的、渐进的、协商一致的、无冲突的演化过程。20世纪,推动社会作别过去继而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前进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的民主机制或经济理性。 [29]
*
对于这一未留下任何余地的断言,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对所有的情形都是真切的。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一结论:一是看是否有参战国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二是拿参战国与那些没有卷入冲突的国家做比较。第一种检验方法操作起来可能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困难。我们已经看到(表5.1和表5.2),就已公开的证据而言,来自所有参战国的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数据资料皆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战争时期出现的极端混乱的局面对矫正不平等具有十足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考察遗漏了部分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和俄国,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在两次大战中都遭受了重创的比利时也是一样,它不能带给我们有关该时期、中东欧这片“血染之地”上各个国家的任何例外信息,“二战”时期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只能说,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此期间曾有国家未出现过明显的矫正现象。依据对收入基尼系数所做的一项并未显示出任何与战争相关的重大变化的简单重构,意大利目前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例外,但很难确定这一例外情况能占有多大的分量。 [30]
至于第二种检验方法,多个中立国家都有“一战”时期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历史证据。1914—1916年,荷兰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21%升至28%,激增了1/3,直至1918年时才回落到22%。在战争早期,高额的垄断利润和股息对此负有责任,但很快它们就因原材料短缺而得到控制。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荷兰最终也未能逃脱动员民众和提高公共支出的需要:政府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一倍,军队规模从20000人扩张到45000人,同时还不得不实施了管理食品生产和分配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设立新的税种来为战争融资,其中包括高度累进的国防税,以及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估计占到战争利润30%的特殊税种。这些措施很快便对早期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势头产生了抑制作用。类似地,瑞典的顶层收入份额先是在“一战”期间突然上升,接着在1920年时急剧下降,丹麦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曾在1917年或1918年时爆炸式地蹿升至28%这样一个异常的水平。丹麦政府实施价格和租金控制的步伐较慢,并且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受一项直到1916年才宣告失效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备受压制。相应地,税收也只是出现了十分微弱的增长。(有关挪威在这些年份中的收入份额,缺乏可用的数据资料。 [31] )
相比之下,“二战”时期少数几个幸免于冲突的国家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冰岛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8—1945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数据的可分解性很差。人们通常以为,战时的价格和工资控制以及原材料短缺促成了这一情况。这一时期,葡萄牙最高收入阶层的份额下降情况甚至更为严重:顶层1%群体在1941—1946年丧失了其收入份额中的40%,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解释。西班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经历了显著的矫正过程。我会在下一章中把它作为内战引发矫正的一个例子加以讨论。 [32]
若暂时撇开后面要详加讨论的瑞典和瑞士,那么,有关“二战”时期非参战国情况的其他证据就所剩无几了。在非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当时仍处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已经独立了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而有关那里的证据资料十分匮乏。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两个极有价值的洞见。第一个洞见涉及收入不平等在阿根廷表现出来的异乎常规的演化路径,该国在20世纪早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二战”时期比战前和战后的都要高。这个结果可与“一战”时期在欧洲几个中立国中观察到的情况相比,当时得益于战争利润,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得到提升。20世纪4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的驱动之下经历了快速增长:英国消费的谷物和肉类中有40%由该国供应。由于阿根廷的精英阶层从对外贸易中不成比例地获利,所以其顶层收入份额与贸易额之间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遥远的战争不仅使它没必要实施军事动员和支持性的财政政策,还压制资本收益率,反而促成了其不平等程度的短期上升,而这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些卷入了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个洞见源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察,即所有有相关信息资料可查的拉美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都很高,这也是我们能据以做系统性比较分析的最早时间段。就曾经计算过该时期标准化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15个国家而言,其计算值分布于0.4~0.76之间,且平均值高达0.51,中位值为0.49。类似地,定性证据也与战争早期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观点不相吻合。尽管看起来智利在“二战”时期经历了不平等的显著缩减,但已有研究将其归因于国内特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战”之后,工资不平等在多个拉美国家呈上升之势,这与欧洲、北美以及日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3]
一份有关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调查资料也表明,这些国家独立时期的顶层收入份额,与西方国家刚刚在“二战”中被降低的标准相比,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一些例外情形仅仅有助于突出战争影响的重要性。印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的缩减超过了1/3。由于源自累退性间接税的财政收入随进口量的缩减而不断减少,印度政府最终选择把针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收的累进性直接税置于优先地位。加在最高收入者身上的累进所得税,以及加在企业超额利润上的附加税,都达到66%。其结果是,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38年和1939年时的23%上升到1944年和1945年时的68%,增长了两倍;鉴于它的税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人,发生这一变化是以牺牲社会上层的利益为代价的。与此同时,工会成员大约增加了一倍,且因补偿纠纷而起的停工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 [34]
再来说毛里求斯,其在1932年时设立了一项所得税,1938—1946年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近2/3。与战时增税同时发生的,是精英阶层总收入和净收入份额的巨大变化。1933年,其顶层0.1%群体在国民总收入和净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什么差别,前者为8.1%,后者为7.6%,但等到1947年时分别下降到4.4%和2.9%,这不仅是精英阶层收入普遍下降的明证,更是财政转移支付导致矫平结果的明证。曾一度处于日本掠夺性占领之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顶层收入份额在1945年之后也很低,具体水平与毛里求斯的类似,而后者的水平又与同期的英国和美国大致相当。 [35]
我们接着将目光转向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非参战国的瑞士和瑞典。它们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反映了作为旁观者的中立国,卷入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高度可能性与国内具体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决定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发展的。1914年,人口只有400多万的瑞士,动员的士兵达到22万人。因为缺少有效的补偿和就业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又与富人们大发战争财的局面一起,导致了劳工阶层的激进化,这一情势最终在1918年11月出现的罢工潮和国内军事部署中达到极致。通过对收入、财富和战争利润加征战争税,联邦政府、各州以及各社区的总收益在战争期间翻了一番,不过这些税收的税率都维持在比较适度的水平上。战后,为偿还战争债务而提出征收联邦直接所得税以及一次性财富税(最高税率为60%)的议案,都遭到了否决。代替它们作偿还战争债务之用的,是1920年通过的一项更具累进性的新战争税。我们因为缺少1933年以前顶层收入份额方面的信息资料,所以无从确定收入分配是如何受这一经验影响的。有关顶层财富份额的数据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口:资产规模最大的0.5%群体,其财富份额在“一战”期间减少了近1/4。 [36]
1939年,瑞士动员的军队规模达到43万人,足足占了其总人口的1/10,但法国沦陷之后,这一数据减少到12万人。为防止社会紧张局势再度出现,该国从以前的战争中吸取经验,给予军队服役者补偿。这一时期,该国的财政收入以一个比1914年之后的增幅大约低70%的幅度缓慢增长。为支撑这种财政扩张,该国引入了一系列应急性的税种:税率高达相关收益70%的战争利润税,针对个人与合法实体征收的税率分别为3%~4.5%和1.5%的财富税,针对收入课征的最高税率达到9.75%的战争税,以及税率高达15%的股息税。这表明,除了战争利润税这个例外以外,与该时期几个主要参战国征收的同类税收相比,这些税收是温和的,同时其累进强度也不是特别高。新增的联邦开支大部分都源于举债,它们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倍。和“一战”时一样,顶层的财富份额呈下降之势:这一次,顶层0.5%的资产所有者失去了18%的财富份额。与此同时,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并未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1938—1945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只是出现了微小的下降,降幅约为1%,或者其总份额的10%左右。唯有最高收入层(顶层0.01%群体)的份额经历了显著的下降,降幅大约是25%,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回到了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的水平。广而言之,瑞士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3—1973年变动甚微,仅仅是在9.8%~11.7%这个狭小的低值区间内轻微地波动。 [37]
总体而言,战争动员对不平等的影响甚微。像其他地方一样,世界大战带来了直接税的大幅扩张,尽管这往往被说成是一种临时的举措。在这种增长广泛受到抵制的特殊情境下,若没有外部威胁的话,瑞士本来是不可能推行此类政策的。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战争尤其是“二战”所做的动员准备,使得战后民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从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由此瑞士就与战争产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削减收入和财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顶层财富份额的发展轨迹符合这一预期。然而,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该国没有发生战争引致的剧烈震荡,以及相应地没有实施高度累进的征税这一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该国在此一阶段及随后一段时期没有出现显著的收入压缩相一致。我们一旦把瑞士政治和财政体制不同寻常的分权化特征,以及按照国际标准,其当时的顶层收入份额已经很低这些事实考虑在内,那么,其遭受的战时压力相对较小以至未能产生更大的矫正效应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38]
瑞典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期则是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发展变化的(图5.11)。但正如当时许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形式呈现出来的外部冲击,是其施行再分配的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福利国家大幅扩张的关键催化剂。 [39]
我此前已通过将瑞典与丹麦和荷兰的情况做比较,阐明了“一战”时其顶层收入份额曾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处于峰值状态。一方面精英阶层与德国站在一边并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由协约国海上封锁带来的食物短缺以及劳工骚乱使得该国动荡不安。临近战争结束时发生的反饥饿游行,使得警察部门痛下重手。民众的不满为该国出现第一个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在俄国革命日益强劲的影响之下,距离瑞典不远的俄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试探性步伐开始不断加快。战争结束后,受金融危机和失业狂潮的影响,其海外市场彻底崩溃,工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图5.11表明,富人阶层不成比例地遭受了损失,这一点在当时继承性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短时间内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些年份里首次出现了税收的大幅度累进,尽管加在高收入者身上的税率仍然很低(图5.12)。所有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瑞典最初朝着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迈进的步伐,是如何深受其“一战”时期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影响的。 [40]

图5.11 瑞典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903—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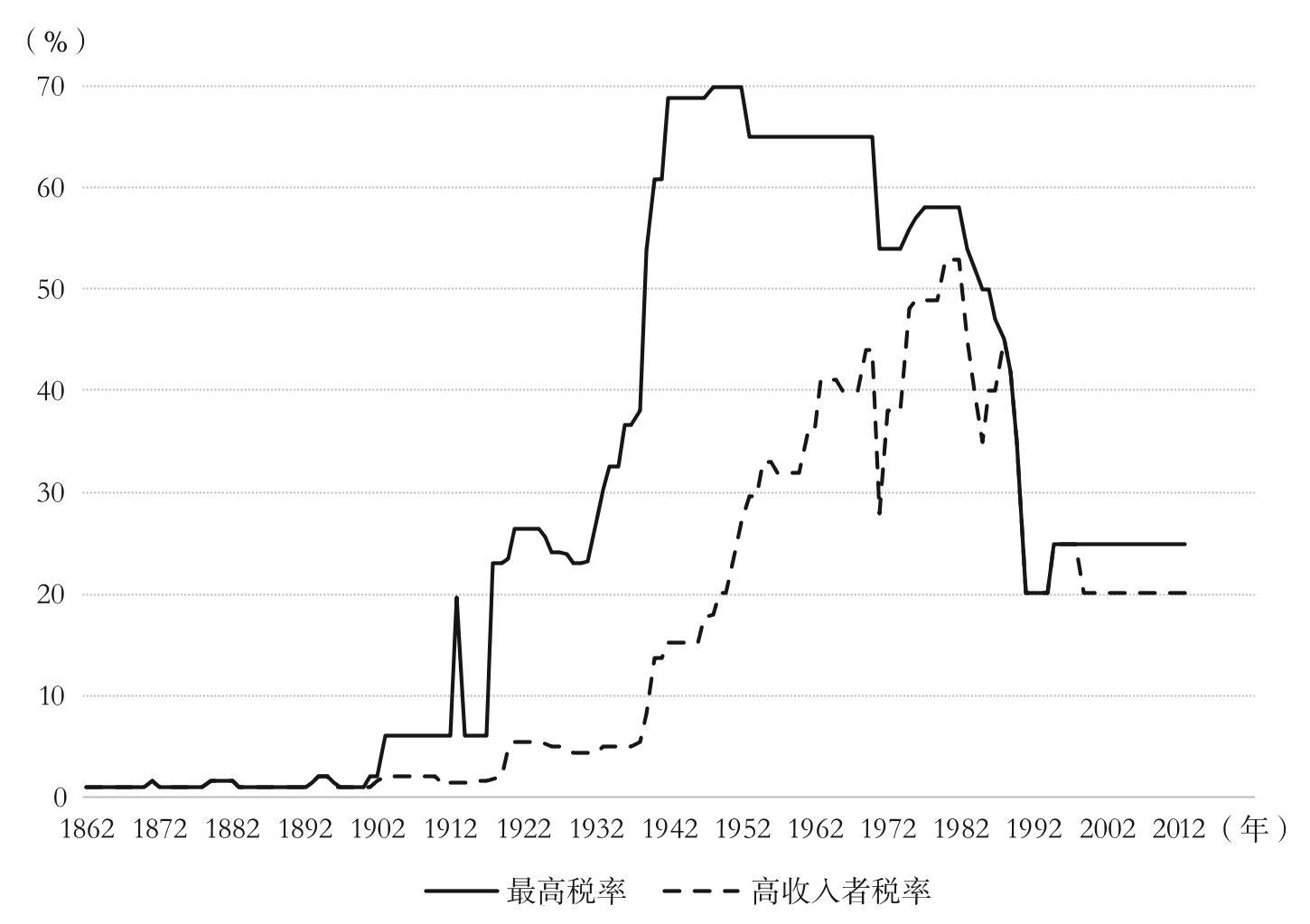
图5.12 瑞典的国家边际所得税率,1862—2013年(以百分数表示)
战争的进一步影响使得瑞典人开始认识到,纳粹战争机器已经转向高速挡。用社会民主党一位头号政治人物1940年时的话说,瑞典人发现他们自己“正活在炮弹满膛的炮口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德国和同盟国的双重压力之下。德国曾一度威胁,除非得到了瑞典的过境特许,否则就对其城市实施轰炸。战争后期,德国曾制订过一份在盟军入侵的情况下也入侵瑞典的临时计划。瑞典基于其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势考虑,实施了大幅度的扩军。军费支出在战争期间增长了8倍。与此前财政政策对大萧条做出的温和反应相比,1939年的税收改革大幅提高了最高税率,同时临时设立了针对最高收入者的高度累进的国防税,其累进区间在1940年和1942年时进一步窄化。此外,法定企业税率升至40%。加强军事力量是官方为所有这些措施给出的理由。拜战争威胁所赐,这些改革得以在未出现多少争端或争议的情况下作为近乎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获得通过,其过程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那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 [41]
然而,其与瑞士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方是,顶层的税前收入份额受战时压力的影响不大,无论我们考虑顶层1%的精英群体还是范围更大的精英阶层,皆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下降,似乎首先是源于大萧条的影响,这个解释与同期的财富份额变化情况也是吻合的。与之相比,“二战”期间并未发现顶层的收入份额有进一步下降,或者顶层财富份额的长期下降呈现加速之势。然而,更早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大幅度平等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更具体地说,恰恰是在战争期间出现了最强劲的矫正,因为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别都在1940—1945年被消除,从而缩小了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信息资料未能反映出这一缩减。 [42]
此外,大规模动员产生的社会影响远不止于财政方面。大规模征兵和志愿性服务将原本属右翼势力的军事力量转变成了一支人民的军队。6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万人服兵役。共享的军事和民用服务,起到了消除既有的猜疑和培育团队协作与互依共济精神的作用。民众的牺牲并不仅止于服兵役本身:大约有5万士兵因受伤、意外事故或恶劣的服役条件致残。定量供应也是导致阶级差别缩小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战争提升了社会同质性,并促进了公民参与。如约翰·吉尔摩在其有关战时瑞典的里程碑式研究中所说:
(这个国家)因战时环境的影响而经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重大变局,并且在1945年时呈现出国民态度和志向焕然一新的景象……其战争时期的征兵实践……为佩尔·阿尔宾以“人民家园”为名的那种社会平等理想,提供了一个模型。瑞典既从战争中收获了社会效益,又没有遭受参战国和被占领国所遭受的那种生命与财产损失。 [43]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动员确实对瑞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后来福利国家的扩张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长远地看,其战争年代的经历还被认为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影响:瑞典曾经因组建联合政府和达成社会共识而将那种小国政治愿景保存下来,对其塑造一种由再分配性福利国家维系的、高度团结的社会理想来说,功不可没。 [44]
战后的政策实践是建立在战时的税收体制以及全民共有的战争经历基础上的。1944年,战争临近结束之时,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联盟一道提出了一个旨在通过累进性征税实现收入和财富平等化的政策纲领。它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政治承诺的一部分,其有如下目的。
将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所有者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合作性的市民共同体取代基于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秩序。 [45]
该国1947—1948年的预算提案提出,要将支出规模提高到原来的两倍以上,因为这是使其恢复到战前水平所必需的。尽管部分预算被指定用于偿付战争债务,但它也使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成为可能。税率从战时的峰值上下降了一些,但所得税的减少将被更高的财富和资产税抵销,这意味着更多的负担被转嫁到富人身上。社会民主党的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福什曾以美国和英国为模板指出,资产税会损害富豪的利益:新设定的最高遗产税率为47.5%,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50%。这项提案几乎完全是从再分配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且论辩甚是激烈。在深受战争体验影响的选民意志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最终胜出,瑞典由此而踏入了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之旅。1948年时,战时的改革举措实际上被常态化了,矫正的步伐得以重启。 [46]
正如那些战争停止后继续保持着高税收和高支出的参战国的情况一样,这一过程的发生与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某些政治党派和劳工联盟,很早便倡导要实施再分配性政策以及缩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帮助这些理想变成现实的催化剂。举瑞典这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战争动员即使只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影响,那也足以促进进步性的政策偏好胜出所必需的财政制度基础、政治意愿和选民支持的产生。 [47]
这一点对世界大战中交战的那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将这些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一系列事件,带来了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继而使战时的矫正作用得到维持,在一些国家甚至被进一步加强:资本因物质破坏、征用或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资本收益因税收以及租金、价格、工资和股息控制等政策干预而出现的下降;以及在战后继续得到维持的高额的累进征税。以各国所具备的具体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为转移,矫正既可能突然发生也可能渐进发生,既可能集中于战争期间也可能拖延至战后乃至更久。但无论它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是在战争期间被占领还是在战后被占领,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政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为大规模暴力所做的大规模动员,构成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跨国性转变的原动力。
我们要感谢皮凯蒂为不平等为什么没在1945年之后快速恢复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资本积累是一个很耗时间的过程,19世纪的西方世界,大部分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事实证明,资本在世界大战中被大规模摧毁之后,只要累进性的收入和资产征税这类战时政策依然保持不变,那么,重建它就要困难得多。并且,这些政策是在各国从高度膨胀的战争状态转向战后社会状态时被保留下来的,最初被用来为战争做大规模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动员的财政政策工具,转而成了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 [48]
战争动员还起到了促进劳工联合的作用。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的工会参与率有助于维持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和保护工人权利,故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矫正力量,并且长远地看,它的确与收入不平等呈反向关系。尽管如此,鉴于工会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战争动员的结果,所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将前者视为导致收入压缩的一个独立的原因。战争动员的重要影响在英国的例子中清晰可见,该国的工会成员人数在“一战”及随后几年大约翻了两番,接着出现了近14年的持续下滑,直到“二战”时才恢复到以前的峰值。在美国,工会参与率先短暂地上升,接着在“一战”时开始回落,继而又因两方面的冲击而激增。一方面,大萧条带来的冲击最终促成了新政的出现以及1935年7月《全国劳工关系法》的出台,该法旨在保障工人组建工会和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工会参与率的早期上涌浪潮已平息多年之后,战争再次为之注入了强劲的上升动力,结果工会成员人数在1945年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稳步地下降。这种模式中的关键要素不断地在发达国家重复出现:工会参与率先在“一战”之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接着在这场大战的后期及随后几年里大幅上升,继而是一定程度地下降,最后又在“二战”时期强势反弹并达到新的峰值。有意义的差别仅在于,战后,工会成员人数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很快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长期保持稳定,且直到最近才开始下降。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的工会成员人数,经历了比“二战”时期更大和更持久的增长,丹麦和瑞典等最明显。图5.13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平均值,很好地显示了这一总体趋势。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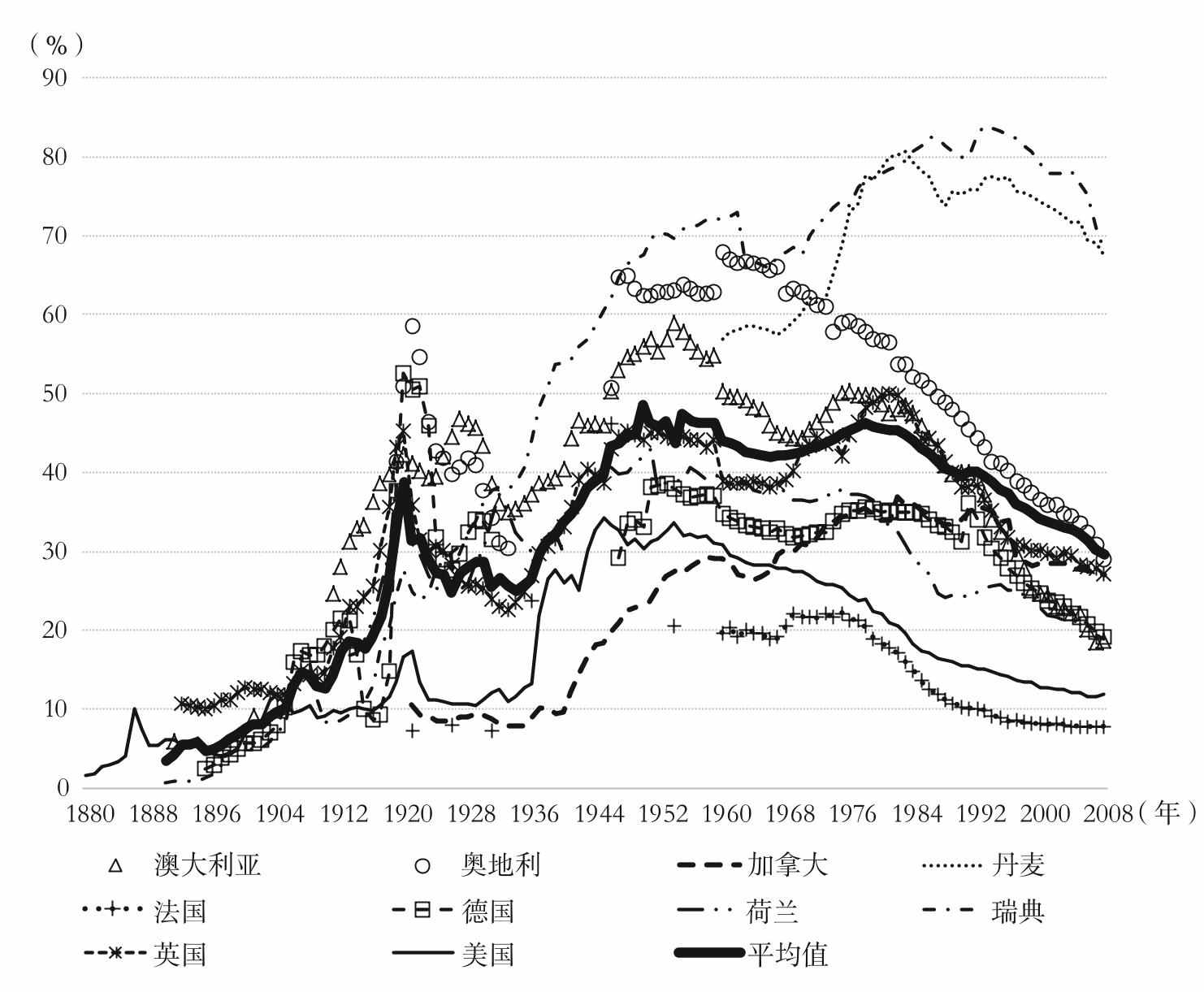
图5.13 10个OECD成员的工会密度,1880—2008年(以百分数表示)
工会人数在经历了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幅扩张之后,与累进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规制一起,起到了防止不平等恢复原状的矫正作用。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中看到的,与劳工联合不同,民主制并非总是与不平等相关。尽管如此,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大战是与选举权的扩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斯·韦伯已指明了其内在的机制:
民主化的基础在社会的任何地方都带有纯粹军事化的性质……军事纪律暗含着民主的胜利,因为军队这个共同体希望也必须确保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所以把武器以及与武器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 [50]
自此,现代学术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大规模战争与政治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就建立大规模的军队需要社会达成共识这一点而言,选举权的扩大化可以被视作高强度军事动员的一个逻辑推论。正如我在下一章要论述的,这个原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运用。就更晚近的历史而言,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所有25岁及以上的男性都有选举议会成员的权利。就确立男性普选权的时间而言,瑞士是在一场各州间的内战刚刚结束后的1948年,美国是在内战结束后的1868年(黑人男性获得选举权是在1870年),德国是在德法战争之后的1871年,芬兰则是在俄日战争引发的改革之后的1906年。选举权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之所以只实现了更为有限的扩张,按照现有的解释,是源于对动乱和可能爆发的革命的担忧。相比之下,与战争或暴力威胁无关的历史案例十分少见。广而言之,1815年之后欧洲出现的和平状态阻滞了政治变革的步伐。这一局面因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规模空前的军事动员而大为改观。1917年在荷兰,1918年在比利时、冰岛、意大利以及英国,全部男性被赋予选举权。普选权上升为一项法律则先后出现在1915年的丹麦,1918年的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和(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1919年的德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典,1920年母语为英语的加拿大、美国、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的爱尔兰和立陶宛。在英国,30岁及以上的女性1918年时也被赋予了投票权,并且这一年龄限制在10年后被撤销。接下来的“二战”又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普选制1940年在魁北克,1944年在法国,1945年在意大利,1946年在日本,1947年在中国(随后仅限于台湾地区)和马耳他,以及1948年在比利时和韩国,先后得到确立。大规模战争与大规模参政之间的联系并非只是间接地体现在时间上,它还有更直接的表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把出让女性的选举权“当作一项战争措施”:
(女性的选举权)对成功地控诉我们被卷入其中的这场人类战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已经使女性的伴侣置身于战争之中。难道我们只应将她们视作牺牲、痛苦和伤病的伙伴,而不应视她们为特权和权力的伙伴吗?
可以说,美国1944年为破除只允许白人参加初选的规定而出台法律禁令,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新的舆论反对排斥同样承受了“战时共同牺牲”的少数民族。 [51]
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与选举权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缓的事实是相吻合的,撇开冰岛和英国在1928年时解除了对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不论,这段时期仅有土耳其(1930年)、葡萄牙(从1931—1936年分阶段地实现)和西班牙(1931年)三个国家引入了普选制。人们也注意到了,在那些远离大战以及不需要为大规模动员提供优惠和补偿的国家,民主化的步伐普遍很慢。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为正规的民主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推动力。 [52]
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暴力冲击,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缩小不平等程度。有关这些独特冲击的体验塑造着战后人们的态度。征兵和定量供应被认为是引发变动的无处不在的强有力诱因。在许多受到影响的国家,撤退以及面临轰炸和其他一些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的危险,进一步强化了战争的社会效应,这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广布于全体国民之中的混乱,不仅弱化了阶级差别,还使得人们对公平、参与、包容和承认普遍社会权利的期待愈加迫切,从根本上说,这些期待是与战前那种严重失衡的物质资源分配结构背道而驰的。战时推行的国家计划使得集体主义思想大行其道。许多学者都认为,对建立福利国家来说,世界大战的经历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催化作用。 [53]
“二战”的灾难性大大加快了社会政策的进程,因为政治光谱中的所有党派都开始认识到在战后施行改革以及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必要性,尤为关键的是它们还有助于提振士气。并非偶然的是,就在法国投降以及丘吉尔发表“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的著名预言前几天,《泰晤士报》(一份还算不上进步主义舆论捍卫者的报纸)发表社论指出:
假如我们谈论民主,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只关心民众的投票权而不关心他们的工作权和生存权的民主。假如我们谈论自由,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排斥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假如我们谈论平等,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因社会和经济特权而趋于无效的政治平等。假若我们谈论经济重建,我们指的是平等分配比最大化收益(尽管它同样有必要)更为重要。 [54]
高度累进的征税、工会化以及民主化,是削减不平等的最重要途径。如果像瑞典经济学家杰斯珀·罗伊内和丹尼尔·威登特罗姆在他们有关20世纪顶层收入份额发展演变的权威研究中所说的那样:
宏观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的下降,但政策方面的转变,或许还有整个经济中的劳资回报平衡率变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5]
那就低估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化战争在引发现代社会的矫正作用方面独有的重要性。就政策和经济变化本身是世界大战的产物而论,他们不应该被当作独立起作用的因素。那些导致了物质不平等缩减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这一结果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它无处不在。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在战时发出的大胆呼吁:
对未来的任何建议,虽然都有必要充分运用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但不应该仅限于考虑那些在获得这些经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部门利益。战争正在使每个部门遭到损毁,因此在社会全部范围内运用这些经验,恰逢其时。世界史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时刻正是革命发生的时刻,而不是那些小修小补的时刻。
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都未被充耳不闻。 [56]
此外,尽管经济变化无疑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很大一部分变化同样源于全球性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影响。想一想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提到的:
基本要素市场在1910年后的大矫正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其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那些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而且包括劳动供给增长率的大幅下滑,教育的快速发展,对非熟练工技术偏见的减少,导致美国转向劳动密集型进口并抑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出口的更具反贸易特征的世界经济,以及金融部门的衰退。
后5个方面,有3个都与20世纪前期的军事和政治冲击有着紧密的联系:移民的急剧衰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断以及金融部门相对收益的下降,都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些冲击的结果或表现,而非独立的影响因素。就余下的两种发展而言,鉴于大部分可获得的证据都表明,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溢价和接受更高教育的回报出现了短暂和不连续的下降,所以,教育供应方面的持续改善可能只会逐步地对不平等产生影响。最后一个要素,美国非技术性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不大可能带来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从顶层收入份额以及收入与工资分配到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率和教育回报率,各项不平等指标都出现快速且显著下降的情况。另外,这场“大压缩”产生的影响遍及整个工业化世界,某些时候甚至更远。一些受影响的国家成了移民的来源地,另一些国家则成了移民的目的地;金融部门在其中一部分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大得多,与此同时,它们的不同表现也与其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机会不同有关。而共同之处则在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暴力冲击及其对资本品,对财政、经济和福利政策,以及对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和革命暴力并不只是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平等化的影响,它更是一种决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果的具有超常压倒性的力量。 [57]
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虽然进步政治组织的再分配议程为战时和战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智识与意识形态基础,但政府为更具雄心的社会政策筹措资金并予以实施的意愿和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它们力图做出回应的暴力战争。 [58] 大规模的矫正源自大规模的暴力——以及对未来发生更大规模暴力的担忧。战后,福利国家在铁幕两边出现的扩张,可能受到了西方国家和苏联两大阵营竞争的影响。更具体地说,1960—2010年,18个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发展受到了“冷战”的约束:通过对诸如最高边际税率、工会密集程度以及全球化程度等其他因素施以控制,苏联的相对军事实力与其顶层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看起来,苏联的威胁起到了约束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这一约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消失。在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战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不再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了。 [59]
[1] Quote: “le drame de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que nous venons de gagner ...”: Charles de Gaulle’s speech at Bar-le-Duc, July 28, 1946, quoted from http://mjp.univ-perp.fr/textes/degaulle28071946.htm.For succinct statements of this thesis, see most recently Piketty 2014:146–150; Piketty and Saez 2014: 840;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55–556, 566–567.
[2] 在此处以及后面的内容中,所有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信息都引自WWID。为了保持一致性,我对每个国家都采用了相同的时间段,即1937—1967年。
[3] Argentina 1938/1945, Australia 1938/1945, Canada 1938/1945, Denmark 1908/1918,1938/1945, Finland 1938/1945, France 1905/1918, 1938/1945, Germany 1913/1918(1925),1938/1950, India 1938/1945, Ireland 1938/1945, Japan 1913/1918, 1938/1945, Mauritius 1938/1945, Netherlands 1914/1918, 1938/1946, New Zealand 1938/1945, Norway 1938/1948,Portugal 1938/1945, South Africa 1914/1918, 1938/1945, Spain 1935/1940/1945, Sweden 1912/1919, 1935/1945, Switzerland 1939/1945, United Kingdom 1937/1949 (1%), 1913/1918,1938/1945 (0.1%), United States 1913/1918, 1938/1945.
[4] Smolensky and Plotnick 1993: 6 fig.2, with 43–44, for extrapolated Ginis of about 0.54 in 1931, about 0.51 in 1939, and about 0.41 in 1945 and for documented Ginis of 0.41 ± 0.025 between 1948 and 1980.Atkinson and Morelli 2014: 63 report gross family income Ginis of 0.5 for 1929, 0.447 for 1941, and 0.377 for 1945, likewise followed by stability.For Britain,see Atkinson and Morelli 2014: 61 for a drop from 0.426 in 1938 to 0.355 in 1949, with Milanovic 2016: 73 fig.2.11 for an estimated market income Gini of 0.5 in 1913.For Japan,see herein, p.115 n.1.Among the national data sets collected by Milanovic 2016, only the Netherlands shows a decline in income Ginis between 1962 and 1982 that is comparable in scale to that between 1914 and 1962 (81 fig.2.15).
[5] Fig.5.3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39 fig.7.19 (http://www.uueconomics.se/danielw /Handbook.htm).有关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数据点,参见本书第3章。
[6] 因此,真正称得上局外人的只有挪威,其所有的分散化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All data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72–575 table 7.A2.France: Piketty 2007: 60 fig.3.5.
[7] Fig.5.4 from Piketty 2014: 26 fig.1.2 and 196 fig.5.8; see also 118 fig.5.5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499 fig.7.5 (http://www.uueconomics.se/danielw/Handbook.htm).
[8] Fig.5.6 from Broadberry and Harrison 2005b: 15 table 1.5; Schulze 2005: 84 table 3.9 (AustriaHungary: military expenditure only).
[9] National wealth: Broadberry and Harrison 2005b: 28 table 1.10.Cost: Harrison 1998a: 15–16 table 1.6; Broadberry and Harrison 2005b: 35 table 1.13.换一个说法,这个相同的倍数如果以今天的全球GDP来折算的话,将意味着一笔高达1000万亿美元的损失。GNP/GDP: Germany: Abelshauser 1998: 158 table 4.16.This share falls to 64 percent if foreign contributions are excluded.Japan: Hara 1998: 257 table 6.11.
[10] Piketty 2014: 107; Moriguchi and Saez 2010: 157 table 3C.1.
[11] Taxes: Piketty 2014: 498–499.See also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0: 538 for initially low rates.Fig.5.7 from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56 fig.7.23 (http://www.uueconomics.se/danielw/Handbook.htm).
[12] Fig.5.8 from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10 fig.1.1.
[13] Fig.5.9 from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81 fig.3.9 (for ten mobilization and seven nonmobilization countries in World War I); see also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2: 83.
[14] Political pressure: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0: 530, 534–535; 2012: 82, 84, 100.Pigou 1918: 145 is a classic statement, quoted in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2: 84.See also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202 fig.8.1 on the Google Ngram surge of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equal sacrifice” during the world wars.For public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Sparrow 2011.Manifesto: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0: 531, 535.Quote from 529: “Those who have made fortunes out of the war must pay for the war; and Labour will insist upon heavily graduated taxation with a raising of the exception limit.That is what Labour means by the Conscription of Wealth.” Cf.also 551 for the notion of “conscription if current income above that wha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a paper from 1917.For the notion of equal sacrifice in political debates, see 541.Excess profits: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0: 541–542.Roosevelt quote from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88.Estate taxes: Piketty 2014:508;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0: 548–549.
[15]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83 fig.3.10.
[16] Piketty 2007: 56, 58 fig.3.4; Hautcoeur 2005: 171 table 6.1.Effects of WW1: Hautcoeur 2005:185; Piketty 2007: 60 fig.3.5.
[17] Piketty 2014: 121, 369–370; Piketty 2014: 273 fig.8.2; 275 (capital losses); Piketty 2007:55–57, 60 fig.3.5 (top estates).
[18] Broadberry and Howlett 2005: 217, 227; Atkinson 2007: 96–97, 104 table 4.3; Ohlsson,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6: 26–27 figs.1, 3.
[19] Piketty and Saez 2007, esp.149–156.However, the overall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may have peaked in 1933 due to very high unemployment: Smolensky and Plotnick 1993: 6 fig.2,with Milanovic 2016: 71.For the Great Depression, see herein, chapter 12, p.363.
[20] For taxation in World War I, see esp.Brownlee 2004: 59–72;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49–81.Tax rates: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65, 69–70, 78; Rockof f 2005: 321 table 10.5.Quote: Brownlee 2004: 58.Mehrotra 2013 also considers the World War I shock crucial for the creation of radical laws and as a basis for further fiscal e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Relaxation: Brownlee 2004: 59;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81.
[21] Tax rates: Piketty and Saez 2007: 157; Piketty 2014: 507; Brownlee 2004: 108–119 (quote from 109);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83–108.Interventions and inequality: Goldin and Margo 1992: 16 (quote), 23–24; Piketty and Saez 2007: 215 table 5B.2; and herein, p.137 (Ginis).Executive pay: Frydman and Molloy 2012.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wages fell from 0.44 in 1938 to 0.36 in 1953: Kopczuk, Saez, and Song 2010: 104.前10分位上的人的工资与总体平均工资的比值,以及第90百分位与第50百分位之间的工资差距,皆表明在20世纪40年代只出现过平等化这一种趋势;只有第50百分位与第10百分位工资之间的比例在20世纪40年代剧烈下降之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二次下降: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199 fig.8–2。
[22] Saez and Veall 2007: 301 table 6F.1 and 264 figs.6A.2–3 for visualization.See 232 for the effect of the war.Earnings at the ninetieth percentile as a multiple of the national median fell from 254 percent in 1941 to 168 percent in 1950 and have changed little since: Atkinson and Morelli 2014: 15.The state share of GDP grew from 18.8 percent in 1935 to 26.7 percent in 1945: Smith 1995: 1059 table 2.
[23] Dumke 1991: 125–135; Dell 2007.Fig.5.10 from WWID.For mobilization rates and state share of GDP, see herein, pp.141–142 and Fig.5.9.
[24] Top incomes: Dell 2007: 372; Dumke 1991: 131; Dell 2005: 416.有关顶层收入的证据资料并不支持Baten and Schulz 2005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正主义观点,即德国的不平等状况在“一战”期间并没有加剧。Funding and inflation: Ritschl 2005: 64 table 2.16; Schulze 2005:100 table 3.19; Pamuk 2005: 129 table 4.4.
[25] Dell 2005: 416; 2007: 373; Holtfrerich 1980: 190–191, 76–92, 327, 39–40 table 8, 266, 273,221 table 40, 274, 232–233, 268; Piketty 2014: 503 fig.14.2, 504–505.
[26] Dell 2005: 416–417; 2007: 374–375; Harrison 1998a: 22; Abelshauser 2011: 45 fig.4, 68–69;Piketty 2014: 503 fig.14.2, 504–505; Klausen 1998: 176–177, 189–190.
[27] Top incomes: see herein, p.133.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176–177, 184 (between 1939 and 1950, the real wages of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nd skilled industry workers fell by 23.5 percent and 8 percent, respectively, but rose 6.4 percent for unskilled laborers);Salverda and Atkinson 2007: 454–458;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183–185.
[28] Finland: Jäntti et al.2010: 412 table 8A.1.Denmark: Ohlsson,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6: 28 fig.5; Atkinson and Søgaard 2016: 283–284, 287 fig.10.Norway: Aaberge and Atkinson 2010: 458–459, and see herein, Tables 5.1–2.
[29] Piketty 2014: 146–150,评论指出“两次大战所带来的预算和政治冲击对资本造成的影响,被证明比这两次大战本身更具破坏性”(148)。Quote: Piketty 2014: 275.
[30] Bloodlands: Snyder 2010.For Italy, see Brandolini and Vecchi 2011: 39 fig.8; but cf.Rossi,Toniolo, and Vecchi 2001: 921–922 for possible short-term equalization during both world wars.For Italy’s war economy, see Galassi and Harrison 2005; Zamagni 2005.
[31] Netherlands: Salverda and Atkinson 2007: 441; Dumke 1991: 131; De Jong 2005.Sweden:WWID; Atkinson and Søgaard 2016: 282–283, 287 fig.10.
[32] Nolan 2007: 516 (Ireland); Alvaredo 2010b: 567–568 (Portugal).For Spain, see herein, chapter 6, pp.204–206.
[33] Argentina: Alvaredo 2010a: 267–269, 272 fig.6.6.For the rapid leveling that occurred between 1948 and 1953, see herein, chapter 13, p.380.Latin American Ginis from SWIID:Argentina 39.5 (1961), Bolivia 42.3 (1968), Brazil 48.8 (Brazil), Chile 44.0 (1968), Colombia 49.8 (1962), Costa Rica 47.8 (1961), Ecuador 46.3 (1968), El Salvador 62.1 (1961), Honduras 54.1 (1968), Jamaica 69.1 (1968), Mexico 49.8 (1963), Panama 76.0 (1960), Peru 53.3 (1961),Uruguay 43.0 (1967), Venezuela 45.1 (1962).For wartime developments, see herein, chapter 13, p.379.Rodríguez Weber 2015: 8 fig.2, 19–24 (Chile); Frankema 2012: 48–49 (wage inequality).
[34] Colonies: Atkinson 2014b.India: Raghavan 2016: 331, 341–344.然而,这一加在富人身上的压力因为战争驱动的价格膨胀而被抵消,后者在使产业资本家和大地主受益的同时,损害了中产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348–350)。For longer-term trends, see Banerjee and Piketty 2010: 11–13.
[35] Atkinson n.d.22, 28 fig.5.
[36] Zala 2014: 495–498, 502; Oechslin 1967: 75–97, 112; Dell, Piketty, and Saez 2007: 486 table 11.3.
[37] Zala 2014: 524–525; Oechslin 1967: 150 table 43, 152–160; Grütter 1968: 16, 22; Dell,Piketty, and Saez 2007: 486 table 11.3.
[38] Oechslin 1967: 236, 239; Grütter 1968: 23; Zala 2014: 534–535; Dell, Piketty, and Saez 2007: 494.
[39] Fig.5.11 from WWID.
[40] Gilmour 2010: 8–10; Hamilton 1989: 158–162;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0: 310; Ohlsson,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4: 28 fig.1.Wage differentials also fell in those years, as agricultural incomes were strong and administrative wages lost ground: Söderberg 1991:86–87.Fig.5.12 from Stenkula, Johansson, and Du Rietz 2014: 174 fig.2 (adapted here using data kindly provided by Mikael Stenkula); and cf.177 fig.4 including local income taxes, for a similar picture overall.Cf.also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8: 381.这里不宜追随Ohlsson,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6: 20或者Henrekson and Wal-denström 2014:12的说法,它们简单地声称,瑞士因为没有参与世界大战所以也没有遭遇严重的冲击——与战争近在咫尺,各种外在的威胁,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强制性因素,也会引发显著的军事动员——只不过规模比参战国更小而已。
[41] Gilmour 2010: 49 (quote), 47–48, 229–230, 241–242; Hamilton 1989: 179; Fig.5.12;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0: 323 fig.7.9; Stenkula, Johansson, and Du Rietz 2014: 178; Du Rietz, Johansson, and Stenkula 2014: 5–6.Consensus: Du Rietz, Johansson, and Stenkula 2013: 16–17.(This information was omitted from the final version in Stenkula, Johansson,and Du Rietz 2014).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动荡不安之后,战时联合政府的成立带来了社会稳定: Gilmour 2010: 238–239; cf.also Hamilton 1989: 172–177。
[42]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0: 320 fig.7.8; Ohlsson,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4: 28 fig.1.The top 1 percent wealth share in Sweden, as computed from wealth taxation, slid down at fairly steady rates for about four decades starting in 1930: Ohlsson,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6: fig.7.Waldenström 2015: 11–12, 34–35 figs.6–7确认了两种结构性的突变,即20世纪30年代国民财富与收入比(从“一战”时候一个较小的值开始)的突然变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早期私人财富与收入比的突然变动,并指出,这些“发生突变的时间节点充分说明,随世界大战而来的政治制度变化,对总体财富与收入比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和战争本身的影响一样强,长远来看尤为如此”(12)。Gustafsson and Johansson 2003: 205论证指出,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哥德堡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稳步下降之势,其主要驱动因素是1925—1936年间资本收益的下降和分散化,以及1936—1947年间加征的所得税。Equalization: Bentzel 1952; Spant 1981.For substantial equalization across income groups, see Bergh 2011: fig.3 as reproduced from Bentzel 1952.Wages: Gärtner and Prado 2012: 13, 24 graph 4, 15, 26 graph 7.Agricultural wages rose because they were exempted from wage stabilization: Klausen 1998: 100.The share of capital income in top incomes collapsed between 1935 and 1951: see herein, Fig.2.6.
[43] Gilmour 2010: 234–235, 245–249, 267.See also Klausen 1998: 95–107.Quotes: Gilmour 2010: 238, 250, 267.Grimnes 2013 describes similar developments in occupied Norway.
[44] Östling 2013: 191.
[45] Du Rietz, Henrekson, and Waldenström 2012: 12.Quote from the “Post-War Program” of 1944,in Hamilton 1989: 180.Cf.also Klausen 1998: 132.
[46] Lodin 2011: 29–30, 32; Du Rietz, Henrekson, and Waldenström 2012: 33 fig.6; Du Rietz,Johansson, and Stenkula 2013: 17.The wartime 40 percent corporate tax had already been made permanent in 1947: Du Rietz, Johansson, and Stenkula 2014: 6.
[47] “这一发展强化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可接受的税收负担在危机时期应该上调,并且这种接受高税率的态度在危机之后继续得到了维持,从而使得税率和公共支出的调节作用逐步加强”(Stenkula, Johansson and Du Rietz 2014: 180)。与之相反, Henrekson and Waldenström 2014试图否认战争的影响,并把政策变化归因于意识形态因素——但这无法解释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何能够实施雄心勃勃的政策计划。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08:380—382试图说明税收在引发战后顶层收入份额下降方面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48] Piketty 2014: 368–375.资产税对财富转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争期间,法国的继承性财产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出现了从20~25%到5%以下的大幅度下滑(380页图11.1)。Dell 2005比较了法国(在这里,战争带来的严重冲击以及战后税收的高度累进性大大削弱了财富积累的进程,并阻碍了这一情势的逆转)、德国(该国也遭受了战争冲击,但选择了累进性更低的税收制度,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集中),以及瑞士(该国幸免于大的冲击,且几乎没有实施累进性的征税,但财富不平等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的情况;也可参见Piketty 2014: 419–421。从顶层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来看,战后,此前的参战国中唯有芬兰没出现矫正现象:经历了1938—1947年间持续而可观的矫正之后,该国的顶层收入份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显著的恢复,与之相伴的是收入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时,该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才降至比20世纪40年代后期更低的水平,但其基尼系数从未到过这么低的水平(WWID; Jäntti et al .2010: 412–413表8A.1)。税收负担在“二战”期间大幅增加,但随征税门槛不断升高,一般民众的税收负担逐渐减轻,并且实际缴税的人口比例随后不断下降: Jäntti et al.2010: 384图8.3(b);and see also Virén 2000: 8 fig.6 for a decline in the gross tax rate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It is unclear how this would have bolstered top incomes.Fiscal instruments: Piketty 2014: 474–479.See 475 fig.13.1 on the state’s share in GDP: in France, the UK,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hare of taxes in national income tripled between 1910 and 1950, followed by different trends ranging from stag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growth by another half (in France).This established a new equilibrium, with much of states’ budgets eventually committed to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replacement incomes and transfers (477).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555–556, 567 likewise consider high marginal tax rates to be a crucial determinant of low postwar inequality.It is not much of an exaggeration for Piketty 2011: 10 to say that “the 1914–1945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hocks generated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anti-capital policies, which had a much larger impact on private wealth than the wars themselves.”
[49] Scheve and Stasavage 2009: 218, 235; but cf.218–219, 235 on the question of causation.See also Salverda and Checchi 2015: 1618–1619.UK: Lindsay 2003.Fig.5.13 from http://www.waelde.com/UnionDensity (slight discontinuities around 1960 are a function of shift between datasets).For detailed statistics see esp.Visser 1989.
[50] Weber 1950: 325–326.Andreski 1968: 20–74, esp.73,对于给定的人口来说,社会分层的程度与军事参与程度是负相关的。
[51] Link: Ticchi and Vindigni 2008: 4 provide references.For a scheme, never implemented,to create a new constitution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coincided with the Levée en Masse in France in 1793, see 23 and n.46.Responses: e.g.,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1182–1186; Aidt and Jensen 2011, esp.31.Other instances: universal suffrage was enacted in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Norway prior to World War I.Peace:Ticchi and Vindigni 2008: 23–24.Quotes in Ticchi and Vindigni 2008: 29 n.27, 30 n.38.For the world wars and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 see, e.g., Markof f 1996b: 73–79; Alesina and Glaeser 2004:220.Mansfield and Snyder 2010’s发现,战争对民主化的影响至多是零散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没能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与其他类型的冲突区分开来。
[52] Ticchi and Vindigni 2008: 30, with references, especially concerning Latin America.
[53] 这种联系被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与战争有关的社会团结、平等的理念,有关充分就业和参与工会会使工人阶级信心大增的政治共识,国家支出和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政府承诺在战后实施改革所带来的士气大振。Titmuss 1958是一个经典表述(有关围绕其立场展开的论辩,Laybourn 1995: 209–210提供了一个简述)。在最近的研究中,Klausen 1998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来说明“二战”对于战后各国创立福利国家的重要意义,Fraser 2009: 246–248就英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Kasza 2002: 422–428则提供了日本的例证; 后者还简明扼要地厘清了大规模战争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对身体健康的士兵和工人的需求、缺乏可以养家糊口的男性公民、对社会正义和精英阶层也必须平等做出牺牲的诉求,以及战争引致的紧急状态等因素的重要性(429–431)。可进一步参见Briggs 1961;Wilensky 1975: 71–74;Janowitz 1976:36–40; Marwick 1988: 123; Hamilton 1989: 85–87; Lowe 1990; Porter 1994: 179–192,288–289;Goodin and Dryzek 1995;Laybourn 1995: 209–226; Sullivan 1996: 48–49; Dutton 2002: 208–219;Kasza 2002: 428–433; Cowen 2008: 45–59; Estevez-Abe 2008: 103–111; Fraser 2009: 209–218, 245–286;Jabbari 2012: 108–109; Michelmore 2012: 17–19;Wimmer 2014:188–189; Addison 1994。
[54] 《泰晤士报》(The Times),1940年7月1日,转引自Fraser 2009: 358。
[55]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55.
[56] Beveridge1942: 6.
[57]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5: 218 (quote), with 206 for another list of these six factors.Milanovic 2016: 56 table 2.1 argues in a similar vein by differentiating “malign” equalizing forces such as wars, state collapse, and epidemics from “benign” factors, identified as social pressures through politics (exemplified by socialism and trade unions), education, aging,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favor of the low-skilled.Therborn 2013: 155–156 contrives to separate “far-reaching peaceful social reform” from 1945 to about 1980 from the preceding violent shocks.For the curtailment of immigration, see Turchin 2016a: 61–64.As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5: 201 fig.8–3 illustrate, relative salaries in the U.S.financial sector plummeted precisely during World War II after having grown somewhat during the 1930s.For discontinuous changes in U.S.skill premi- ums, see herein, chapter 13, pp.375–376; for unionization rates, see herein, pp.165–167; for the potentially disequalizing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see herein, chapter 16, pp.426–427.
[58] See the literature cited herein, at n.53.Economic policy in particular was sensitive to war effects:to give just one example, Soltow and van Zanden 1998: 195 note that 1918 and 1945 were focal points of public debate about how the Dutch economy should be organized in the Netherlands.Even if Durevall and Henrekson 2011 are right to maintain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growth of the state’s share in GDP was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driven by a ratchet effect of war-related jumps, economic growth by itself cannot account for the emergence of war-driven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that was conducive to sustained leveling.Lindert 2004, who tracks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long term and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alls the 1930s and 1940s a “crucial watershed” when war and fear boosted social democracy (176), even if it took until the 1970s for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welfare systems to have run its course.
[59] Obinger and Schmitt 2011 (welfare state); Albuquerque Sant’Anna 2015 (Cold War).致使苏联的军事实力对顶层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的那些最直接因素(不是边际税率)究竟具有何种性质,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For the future of war, cf.herein, chapter 16, pp.436–439.
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最近在有关税收和战争的研究中,阐释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与前现代战争的断裂。30年战争结束以来,13个主要大国的军事动员率表明,在军事力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同时,动员率却保持在平均约为总人口的1%或1.5%这样一个十分稳定的水平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平均动员率在1900—1950年的半个世纪里暂时性地上升到4%~4.5%,这比此前250年的平均水平高了三倍(图6.1)。与之相契合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是一种既强大又少见的矫正力量:正如我在第3章表明的,在以前的这几个世纪中,若无战争发生,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物质不平等要么不断加剧,要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上。 [1]
在1914年以前,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只是零星地出现过——总人口中有某一显著的比例的人口(比方说至少2%,如舍韦和斯塔萨维奇的分类系统所要求的那样)在军队服役。战争的持久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可能指望短暂的战争潮对私人资源分配产生大的影响。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动员水平无疑是高的,但只持续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且仅仅开战一个半月胜负就已见分晓。早于此10年爆发的美国内战,倒是更有希望成为矫正力量的一个范例。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其界定为一场内战,但它体现出了大规模国际战争所具有的许多特征,并且交战双方都做了广泛的人力动员。1861—1865年间,北方联邦动员了200多万的士兵,大约占其总人口的1/10,而南方邦联从其560万非奴隶人口中组建起来的军队接近100万人,即大概占到该群体人口的1/7甚或1/6,以及南方总人口的1/9——一个意义更小的比值。撇开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不论,这种动员率即便参照后来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与法国和德国在同样持久的“一战”时期高达1/5的动员率相比,南部邦联的动员率并未逊色很多,与此同时,北方联邦的动员率也不比“二战”时美国1/8的动员率低很多,与其“一战”时仅为4%的动员率相比还高出很多。因此,这场内战显然算得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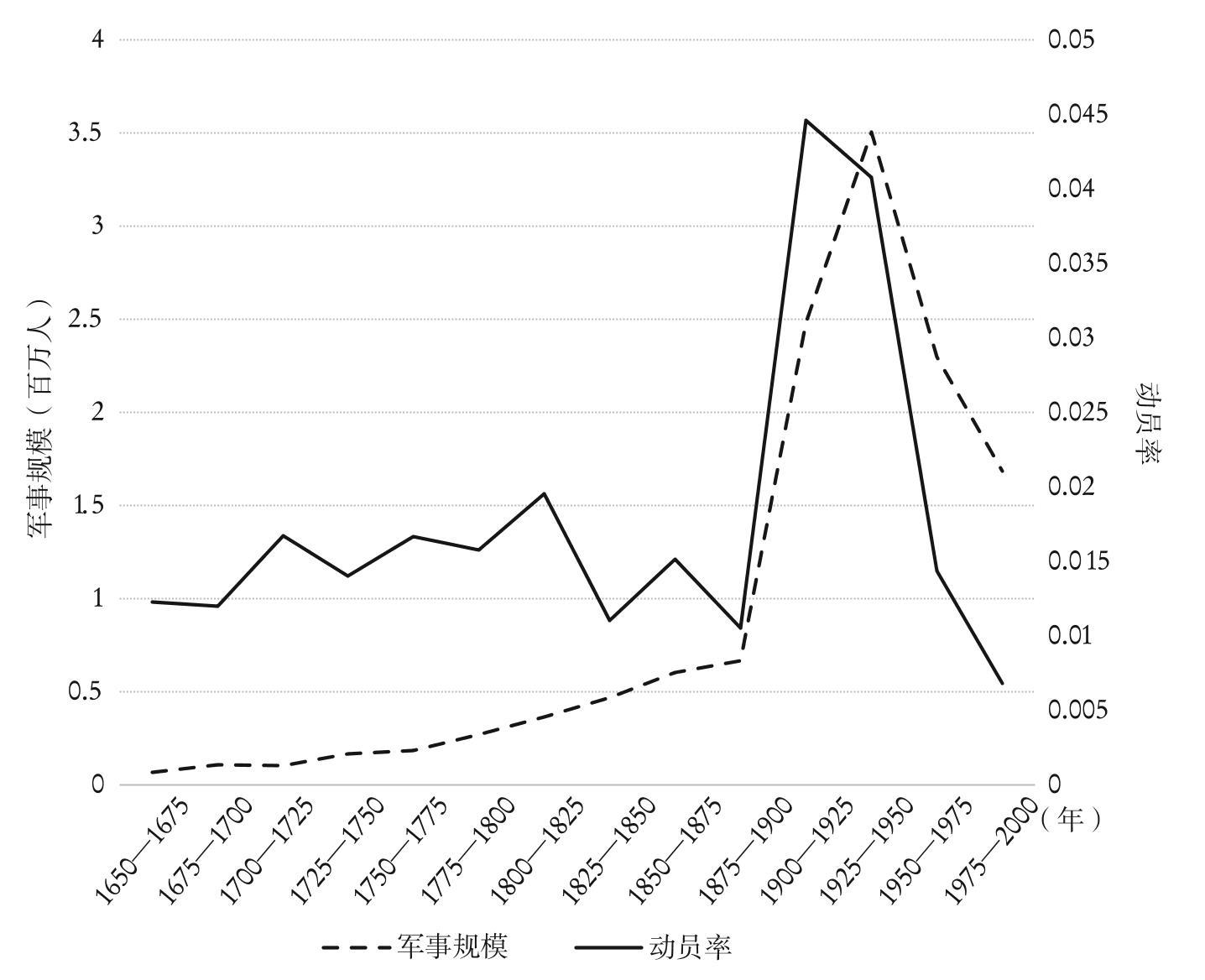
图6.1 大国在战争年份的军事规模和动员率,1650—2000年(每25年的均值)
原则上说,这场战争的关键特征——广泛征兵、经年累月、耗费巨大以及伤亡惨重本该有助于催生那些能产生矫正效果的政策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内战比此前美国领土上发生的其他战争更彻底地改变了财政制度。1862年,北方联邦创立了一项所得税,南方在接下来一年里也紧随其后地实施了该政策。然而,北方联邦最初施行的是一种不仅很低而且累进程度温和的所得税,其加诸大多数应税收入的税率为3%,加诸最高收入的税率是5%。1864年国会设定的税率稍高一些,达到10%,目的是对征兵暴乱和有关公平的社会争论做出回应。即便如此,这项税收依然没能获得多少收入。它最初被用于偿付战争债务,到1872年时宣告失效。本质上是累退性的消费税充当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仅有的一项产生了显著收入的直接税,即针对农产品课征的、实为一种正式征收的什一税,事实上也是累退性的。与此同时,南部邦联主要靠印钞票来维持战争,至战争结束时其失控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9000%。 [3]
这场战争最终对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在南方和北方是迥然不同的。在北方,富人们通过为军队提供给养和承保战争债务获得了巨额利润。19世纪60年代百万富豪的数量大幅增加。约翰·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安德鲁·卡内基这些著名的富豪,最早就是作为战争投机商发家的。或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发生在最顶层的财富集中并未在各种样本调查研究中得到反映,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富不平等程度在1860年和1870年时是高度相似的,同时,源自财产的收入分布,总体而言也只是稍微集中了一些。相比之下,总体收入差距在这个10年里大幅拉开:在新英格兰,收入基尼系数的上升超过了6个百分点,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较此前的上升了一半;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尽管通常更温和,但与之相似的变化。毫无疑问,内战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程度。 [4]
对战败的南方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在那里,奴隶制的废止使得作为精英阶层的种植园主的财富大幅缩减。1860年,南方各州因蓄奴而获得的私人财富份额达到惊人的48.3%,大大超过了所有农庄及其附属建筑物的价值总和。奴隶制使得南方的不平等达到了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的程度:1860年时南大西洋地区各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1,东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5,西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7,这与当时全国0.51的总体基尼系数以及1774年时南部0.46的基尼系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奴隶制相当普遍,南部1/4的家庭都拥有奴隶,但大约有1/4的奴隶集中在0.5%最富有的家庭中。不附带补偿的大规模奴隶解放连同战时的混乱,外加南方各州因战争而普遍遭受的物质破坏,使得区域内的资产大幅缩减,这些损失由那些在种植园主阶级中处于最顶层的人不成比例地负担。 [5]
最为详细的证据资料,来自一份有关1860—1870年情况的样本调查,它可以让我们追踪到美国内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数据记载,南方各州遭受了规模巨大的财富缩减:在这10年中,人均财富下降了62%。这些损失是在不同财富等级和资产类型之间不均匀分布的(表6.1)。 [6]
表6.1 1870年时南方白人的财产相对于1860年时的价值(1860年时的价值=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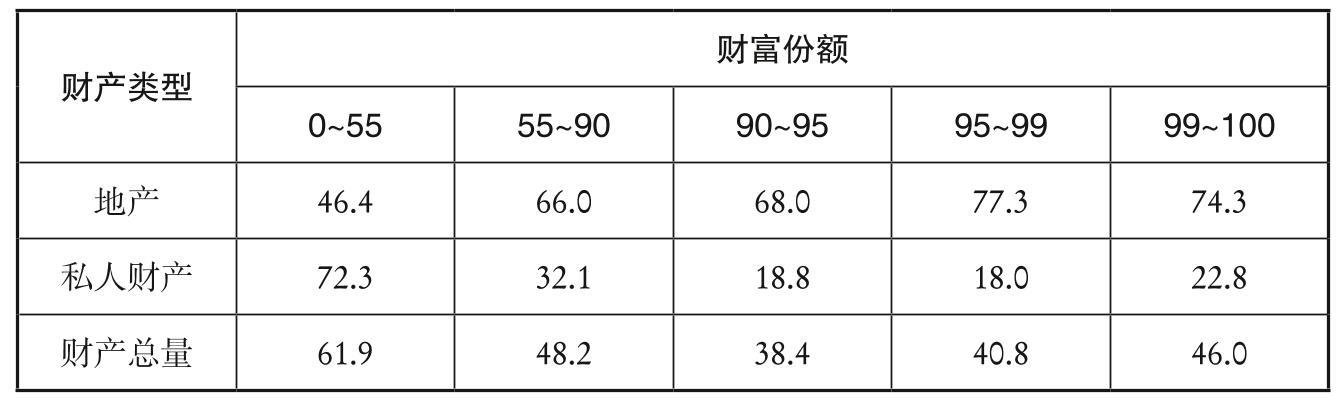
最富有的10%群体与余下的人口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其不动产份额从68.4%轻微上升到71.4%,但它们在个人财产总额中的占比从73%降到59.4%,进而总财富份额从71%下降到67.6%。除最顶端的1%群体外,个人财产的损失程度随财富规模而递增,但那些相对不太富有的人在不动产方面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前者首先要归因于奴隶制的废止,它使得南方社会上层的个人财产损失惨重,而那些原本不拥有奴隶的富人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要不是因为次级富人的不动产发生了更为剧烈的贬值或缩减而部分遭到抵销的话,这一过程对南方社会的矫正效应,本来会大得多。1860—1870年有关南方白人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登记在册的不动产基尼系数仅发生了小幅下降(从0.72降至0.7),但反映个人财产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从0.82到0.68的大幅降低。其结果是,总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下降幅度介乎二者之间,即反映全部资产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从0.79降至0.72。鉴于时间跨度短,这意味着总体不平等程度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即便把被解放了的奴隶包括在1870年的样本中,也不能使这一总体趋势有所不同。
与这一变局相呼应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表6.2)。就南方的全部人口而言,财产收入基尼系数从1860年的0.9降至1870年的0.86。总体上,南方“顶层1%群体”占总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3,同时,区域收入基尼系数大幅缩减了7~9个百分点。 [7]
表6.2 南方家庭收入不平等情况

然而,南方社会出现的矫正,不是源于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本身,而仅仅是源于战败。尽管它看上去像一场最早出现的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尽管它动用了工业资源,并从战略上重视民用基础设施,但就其对物质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来看,这场内战仍然是一场胜者得、败者失的传统战争,与普罗大众相比,胜败双方的精英阶层所得或所失不成比例。我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这一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甚为广泛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时的战争与那种更古老的、公开掠夺式的战争的不同之处仅表现在方式上。就美国内战这个特定的例子而言,其主要结果是财富和权力从南方的种植园主转移到北方资本家手中。由于缺少再分配机制——这一点本身又源于联邦政府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民主制度的相对软弱性,得胜方的财富精英是从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非从夺取南方的资产中获利。战争若是早几个世纪发生,他们便可以径直接管南方种植园或将南方的奴隶据为己有。这个例子中,失败一方的财富精英被没收的财产不是被胜利者直接攫取,而是被无任何返还地征用。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损失规模,因为虽说奴隶得到了解放,但种植园主享有自身劳动成果的权利并未遭到剥夺。
与此同时,与更为传统的、战略野心和破坏潜能更为有限的前现代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全面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财产损失的普遍性,为战败方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烦扰。美国内战是一个混合体,它处在社会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上,一只脚已踏入现代(其表现是大规模的军事参与以及它的影响遍及全国),但另一只脚还留在过去(其表现是胜利方精英不受约束地获取暴利,战败方精英的资产消耗、流失严重)。不平等的结果在胜败两方表现得如此悬殊,这大概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与之相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证据判断,无论其国家胜败如何,精英们普遍都遭受了损失。 [8]
在现代早期发生的其他系列战争中,可以被称作大规模民众动员事件的,仅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战争。1793年,法国的局势异常紧张,与包括匈牙利、英格兰、普鲁士以及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欧洲主要势力都处于交战状态。同年的8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了“告全体国民书”,试图动员所有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未婚健康男性应征入伍。其当时的措辞(随后的实践更是如此)就是有关大规模军事动员的:
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的那一刻,所有法国人都将一直被召唤为军队服务。年轻的男人应该去打仗;已婚的男人应该去制造武器和交通装备;女人要缝制绷带和衣物以及去医院帮忙;儿童要把棉绒纺成棉布;老人应该自己到广场上去,以激起勇士的斗志,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一致。 [9]
历史将表明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一步。当年仅仅13岁便参加抵抗法国的战争,并由此开启了其非凡军事生涯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后来在《战争论》一书的终结篇中这样感叹道:
1793年时出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突然之间战争再度成为这个民族——一个人口达到3000万、人人都视自己为公民的民族的共同事务……国家以其全部的重量被抛到了天平之上。此时,可动用的资源和力量超出了所有常规的限度;现在已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住一触即发的战争势头。 [10]
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军事力量规模空前,且在整个欧洲全线作战。1790—1815年,大约有300万法国人,或者说该国总人口中有1/9都曾在军队服役——这一动员水平堪比内战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从法国革命伊始到“后拿破仑时期”,收入分配被认为稍微变得公平了些。然而,我们无法判断,是该将这一变化更多地归功于国内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征用和再分配,还是该将其更多地归功于法国因对外发动战争而招致的成本和后果。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与革命一前一后到来的情形已出现过数次。德国和“一战”之后的俄国,以及“二战”后的中国,是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先于而非后于大规模战争而来。这使得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矫正效应,只能优先将革命作为一种解释,从而把战争的后果视作革命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会在第8章探讨法国的经验,那一章专门考察的是借助革命途径实现的矫正。 [11]
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至少就我们在前面几页所做的那种定义而言,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人口中至少有1/10的人曾服过兵役。若采取某个更低的门槛,我们也能把拿破仑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中更多的参战国包括在内,并且这样做不会改变事物的总体情形。舍韦和斯塔萨维奇选定的最低门槛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有2%的群体在军队服役,但是,对那些更持久的战争来说,因为士兵会阵亡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被替换掉,所以整体来看,服兵役的人口比例最终会更高。鉴于在前现代时期,传染性疾病是导致军队减员的一个突出因素,所以在一场持久战中,即便要维持这个下限值,也需要更多体格健全的人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单是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这种消耗,更不要说经济、财政和组织方面的限制了。 [12]
一些帝国政体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大,而非因为做了大规模的动员。例如,在公元11世纪,南宋王朝供养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北面金国的威胁。据说,军队的总人数高达125万,军队的俸禄一部分被装进贪官的口袋,而非真正用于增强军事实力,但是,即使是100万人的军队也不超过当时至少1亿总人口的1%。鼎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控制着超过1亿的人口,但服兵役的人甚至不到其中的1%。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可能有6000万~7000万人口,军队规模大概是40万人,远小于总人口的1%。奥斯曼帝国的动员水平甚至更低。 [13]
为了找到更多有用的例子,我们需要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时代。战国时期的中国值得重点考虑。所谓战国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7个主要国家历经军事上的激烈争斗最终实现大一统的这段历史时期。在长期胜负难分的冲突过程中,领土变得越来越集中,与此同时,它们力图将其人口和其他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霸业争夺之中。行政重组有可能对精英权力和物质财富的集中产生影响。为改变此前领土和人口被各地势力雄厚的精英家族作为封地控制着的局面,战国的统治者推行了基于一种特殊区划单位(县)的行政管辖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他们能够直接控制这些区域,进而有能力征税和征兵。为了摧毁世袭贵族的权力,君王们转移、解散甚至处决了一部分官员。原本出自统治阶级家族的高级官员,要从底层精英圈子中遴选产生,并从此只能靠为国家提供服务而获得身份地位和薪俸。最终,由于那些老的权贵家族被取代,大多数官员都出身低微。 [14]
行政重组可能牵涉土地重组: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国家对土地实施了网格化的重组,并按照每5户为1个单元的划分方式对全部住户重新编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巩固了土地私有制,同时还消除了那些此前以抽租或盘剥劳力的形式侵蚀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层精英的势力。这些干预引发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史料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变革是秦朝(始于公元前359年)的商鞅变法,其目的就是要对整个乡村地区实施一种矩形网格化管理。在当地发现的那些笔直的大路和人行道表明,这些野心勃勃的变革计划确实得到了实施。变革者力图将土地划分成同等大小的地块,进而根据每家成年男性人数分配给各个住户。这些计划很大程度上确实得到了实施,它们本可以带来村民之间更均等的财产分配,但军事奖赏制带来了新的贫富差距:秦朝末期,士兵每砍下一个人头就能晋升一级,同时还能获得一份数量固定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产出相当于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标准。另外,封地依然存在,尽管只是作为收入的单位而非实际控制的领地。例如,在秦朝的十几个社会等级中,9个最高等级的成员,收入都来源于此。尽管封地不能世袭,但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购买或者向农民提供贷款使之陷入债务危机来私有化这些土地。 [15]
这一重组的最终目的是供养更庞大的军队,以及获得更多的收益用于战争。农耕人口被看成军事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农民同时也是潜在的士兵的理念,在“耕战治世”这个概念中得到了体现。同样,城乡之间的区分也被打破,所有的人口都被凝聚在一起。这就使此前王公贵族所崇尚的合法暴力行为(主要是战车和狩猎竞赛等仪式性的争斗)得以蔓延到平民百姓之中,后者常常会被征召参与大规模的步兵作战。 [16]
整个战国时期都充斥着军事冲突:按照现代统计,从公元前535—前286年,总共发生了358次军事冲突,或者说,平均每年发生的军事冲突超过一次。这些冲突往往经年累月,且涉及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军事动员的水平很高,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那些报道出来的,经常被夸大了的数据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依据这些数据,齐、秦和楚这几个主要国家,各自可以利用的士兵超过了100万,这或许代表了它们全部可用的人员数量。人们经常会提到那些参战人数超过10万或者更多的战役,并且它们的规模呈不断上升之势。据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赵国的40万军队全部被秦国军队屠杀。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战败国在26场主要战役中的死亡人数高达180万,另外一项调查还显示,在同期的15场战役中,接近150万人被秦军杀害。尽管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是,大规模战争的广泛出现和严重的损耗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震惊的是,在与长平之战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战争中,秦军征召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 [17]
这些战役是否促进了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化,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国家通过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力、启用领薪水的官员以及实行非世袭的封地制度,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并且有助于限制财富的跨代积累。针对平民实施的土地制度缩小了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土地私有制是一把双刃剑。鉴于在此之前农民有着很高的依附性,而且有关土地有效控制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本来就非常高了,所以,赋予私有土地可转让性,最终促进了土地的再次集中,在汉朝早期出现的一些有关秦朝统治的批判性言论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的观察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农民失去土地是由税赋压力以及国家施加的不可预知的服务义务造成的,它们迫使农民先是为了维持资金周转而向富人借出高利贷,接着将土地交由富人接管。常年的战争不仅加快了土地均等化改革和私有化的进程,并且逐渐破坏了随之而来的私人土地制度。这个时期,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城镇从贵族的要塞中转移到更大的城市中。所有这些趋势都预示着不平等程度会与日俱增。它们与史料中的下述记载也是一致的: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雇工或者租户,另一方面商人和企业家等资本所有者购得他们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剩余财富视作万恶之源,需要以无休止的战争加以吸收,也是有道理的。 [18]
然而,不断增加的私人产出不大可能完全被战争吸收。考古学界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发现。一项研究指出,楚国的下层精英和平民在这一阶段实现了融合。之前的那种依据谁有资格在墓穴中放入一些陪葬品来推断当时存在社会分化的考古学观点,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放置同类的陪葬品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现象。由此,社会差距就只体现在了数量方面,如陪葬品的丰富程度或坟墓大小的不同。财富而非等级,成了地位和阶层分化的主要标志。青铜制成的武器广泛见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的墓穴中,这是全民军事化的表现,却未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平均主义的表现。 [19]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是一个多股敌对势力彼此扰攘纷争的竞技场,这些力量之间的竞争既可能抑制也可能助长不平等。这两种作用力不必是同时发生的:早期时候,矫正效应因原有的贵族被取代而出现,然而,随着富人开始采取基于市场交易而非封建特权的再集中策略,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很可能逐渐遭到侵蚀,甚至最终发生了逆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与私人财富的增加同时出现,并且还可能伴随着私人财富的不断积聚。在大规模军事动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对私人资源的掠夺,不可能使私人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势头得到遏止。考虑到这种税收制度给那些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人,即农民施加了沉重的双重税赋(军事劳动和农产品),而其他形式的财富更容易躲过国家的征用,它事实上很可能是累退性的。当时的步兵作战成本相对较低,主要依靠的是征兵、大批量生产的武器(就像后来几个世纪的情况一样,这其中可能涉及施加于囚犯和他国劳工的强迫性劳动),以及农民自产的粮食。秦朝的农业税据说比随后汉朝的农业税要高得多。当时的战争也不需要战船这类昂贵的武器装备,故而也没必要征收更具侵略性和累进性的税赋。因此,我们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将战国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导致再分配的一个成功驱动因素。就这个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与平等化的关联而言,实施再分配措施是发动战争状态的一种方式,而非战争的结果。这一点,对现代时期的世界大战来说,是不适用的。 [20]
罗马共和国的情况几乎也一样,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高水平的军事动员。有关它的军队参与率,很难给出精确的数据。尽管对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这段时期的军事力量,我们掌握了大量可信的信息资料,但罗马市民人口的潜在规模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其历次周期性人口普查记录做出解释。我们对其军事动员率的估计结果,取决于我们是把其中的某些普查记录解释为涵盖全部罗马公民的,不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统计,还是解释为仅仅对成年男性公民人口所做的统计。证据倾向于支持我们对罗马公民人数做出一种保守的估计,而这又意味着其军事动员率总体而言是很高的,甚至某些时候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由此说来,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高潮阶段,罗马或许征用了总人口中的8%~12%,或者说,征用了17~45岁男性人口中的50%~75%。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公元前1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尽管时间很短,服兵役的人口比例仍然达到8%或者9%。而在更长的时期,即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证据表明,罗马大约有一半的男性公民平均服兵役7年。即使我们对罗马的公民总数做出更高的估计,相应得出的更低的军事动员率(可能低一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来说,仍然是很高的。 [21]
但是,再一次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形式的军事参与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起到了限制作用。虽然掌管国家运转的寡头统治者没有大肆掠夺精英的财富,但强制性征兵以及随服兵役而来的周期性疏于农耕的问题,对普通民众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愿意将目标指向富人。公元前214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罗马到了破产甚至土崩瓦解的边缘,军事动员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元老院命令罗马公民交出他们的奴隶以充当海军的划桨手。依据普查结果,按出资大小将其分成若干等级,虽说这种累进制是前后不一致的。那些拥有5万罗马币(当时罗马货币的面额),在7个财产普查等级中处于第4等级的中等收入者,需要提供1个奴隶;那些拥有1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3个,拥有超过3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5个,拥有100万或者更多罗马币的人则需要提供8个。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并没有被要求缴纳与其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成比例的税收,更不要说是直接以一种累进的方式纳税了。因为这一方案而承受了最沉重负担的,是平民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而不是财富精英阶层。即使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罗马的寡头统治阶级也力图做出尽可能少的让步,这和民主政体比如古代雅典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者是通过对富人阶层课以重税来维持战争开支的。 [22]
罗马倾向于依赖其不断扩大的帝国的税收:公元前167年,废除了针对公民家庭财富征收的直接战争税。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财富在统治阶层中大量积累,这是我在第2章已描述过的一种发展。与很久之后美国古南方地区 [01] 所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时期,有几百万的奴隶被输送到意大利,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和收入差距。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的有效控制,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朝贡系统的有力支持,鼎盛时期的罗马共和国能够在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条件下维持其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我将在这一章的末尾处阐明,对这一过程来说,一种可能出现的、最多只能算是短命的例外情形是什么。
这样一来,迄今为止,在奉行平等主义以及对与广泛的民众军事参与相关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施加限制方面,最适合作为典范的历史先例就只剩下一个了:古希腊的例子。公元前2000年末期,在青铜时代的那种更大和更集权化的政体被摧毁,广泛的等级制和经济不平等被矫正(如第9章所述)之后,剧烈的政治分化开始在希腊出现。从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是史上最大的城邦文化,其最终形成了1000个独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总人口达到了700万甚至更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城邦:在有历史资料可查的672个城邦中,领土面积在20~40平方英里的很常见。尽管在历史记载中,以雅典为首的那些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城邦受到不成比例的关注,但有理由认为,一般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的那些城邦政体中也是广为人知的。 [23]
对好几代研究者来说,多元体制的出现和巩固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由于缺乏这一早期形成阶段的证据资料,很多研究都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这种多元体制似乎是按照乔塞亚·奥伯最近提出的那种城邦演变模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牵涉三个问题:为什么旧政体瓦解之后,那些统治者不能再创造出更加集权的社会秩序,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小政体,以及为什么政治权威会变得如此分散?奥伯论证地指出,不利于合并成帝国的地理条件、铜器时代超乎寻常的崩溃程度、有助于促进武器使用民主化的铁器技术的推广等三大因素加在一起,“在原有的那种相对比较熟悉的城市国家道路基础之上,共同催生出了一种国家构成方式的独特变体,即一种高度公民本位的国家生成路径”,这种新的路径最终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继铜器时代崩溃之后到来的铁器时代早期,社会共同体是很贫穷并且是相对未分化的,尽管后来的精英阶层试图在人口和经济增长复苏之后重建等级制,但平均主义规范仍然在一些共同体中得到维持,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共同体的竞争中胜出。
奥伯认为,正是因为铁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以及当时流行的是十分简单的步兵战模式,所以,“决定共同体该动用多少人参入战争的是一种社会选择过程,而不是共同体所面临的经济约束”。他还认为,“在这些条件下,高动员率和高士气与公民本位的制度形式呈正相关,而与排他性的精英小团体统治模式呈负相关”。换言之,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容易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单个城邦通过吸纳竞争能力更弱的城邦来实现扩展自身的举动,会受到那种同样也旨在提升城邦竞争力的公民社会规范的制约。尽管持续的经济扩张,特别是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构成了削弱平等主义规范的潜在威胁,但能否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战,仍然是决定国家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考虑下述因素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作战的主要方式是打方阵战,其成熟形态即一种直线合围的布阵模式,攻击力主要取决于方阵的大小。方阵战模式为在精英圈子之外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在长矛和盾牌这类基本武器装备的数量足够供人们作战使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4]
尽管学界还未对战术和政治机构演变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做出定论,但很明显,到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已形成了一种与大规模参与步兵作战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文化。军事贡献的广泛共同承担,与在特定领域中彼此平等相待的公民实体的广泛形成结伴而生。城邦的治理因一种强有力的非职业性要素的参与而得到加强,由此形成的公民权利传统,既有助于公民免受那些有权势者的压迫,也有助于遏制政府的权力。尽管各城邦的具体政治实践形式沿着从独裁统治、寡头政治到民主制度这一范围广泛的谱系并彼此有异,平等主义统治仍然是这一系统的标志性特征。 [25]
这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化呢?通过对古代文字证据做字面上的解读,看起来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出自最好战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根据经典的解说,早期的斯巴达实施了一系列与一个名叫莱克格斯的立法者联系在一起的广泛改革。这些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为著名的结果是高度平均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它要求所有人,包括高级领导者在内,每天都必须到某个小群体食堂集体就餐,吃的各种食物由所有成员共同提供,且每个人提供的分量相同。这个立法者据说还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施行了平均化改革:
他说服公民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接着再重新分配,然后他们就靠相同的平均份额来生活,用等量的财产来养活每个人。 [26]
在斯巴达的中心地区拉科尼亚,据说全部的农用土地被平均分割成30000块,其中的9000块分给了斯巴达的男性公民。负责耕种的是希洛人,他们是公民集体所有的奴隶,常年在农奴制条件下耕作,并依附于这些土地。这种安排既是为了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也是为了确保公民除了从事军事活动之外不必再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可移动的财产也要予以再分配,私藏稀有金属货币的行为是被禁止的,禁奢令还要求人们不得投资私人住宅。公民经历了高强度的军事动员:几乎所有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在7~29岁之间,都必须接受一种集体的军国主义教育,其训练方案着重强调的是忍耐和剥夺。这种制度,就其要求公民个体为争夺荣誉和地位而相互对抗而言,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高度平等的,它甚至还要求女孩子接受一种强调身体技能的公共教育——这在前现代社会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安排旨在塑造一支平等的公民队伍,以便最大化其军事力量。据说,正是这些规范成就了斯巴达势力的持续扩张;最显著的例证是,公元前19世纪时,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的美塞尼亚人,并将他们贬为奴隶;这不仅带来了公民土地份额的进一步调整,而且为斯巴达人在随后一个世纪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主导的联盟系统准备了条件。远古的历史记载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持续存在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状态,对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影响,并且与一种同样也宰制着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主义规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对致力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矫正效应的现代学者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后世的外部钦慕者所做的风格化描述的社会传统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无从判断这种理想化的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自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前4世纪之后,不断加剧的资源不平等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考虑到后者并不排斥前者,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明显缺乏某些能够对不断更新的不平等状况做出周期性调整的机制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从一种财富均等分配的初始状态逐渐走向某种更不均等的结果。但问题是,后来的这些状态究竟是全新的,还是仅仅表示早期发生的经济分化的持续恶化。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最为透彻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财产在斯巴达人当中的分配一直都是不平等的,且本质上具有私有性,但同时又受到了一种追求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公共意识形态的制约。毫无疑问,可能会出现土地份额跨代传递的情况,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即便初始状态十分均等,也会不断拉大不平等的机制。斯巴达人在财产继承方面所采用的特定惯例,带来了土地和其他财产在其公民之中的加速集中。当一些斯巴达人的财产不够为公共食堂提供所要求的那种标准化贡献时,他们就会失去作为完整公民的地位,所以,财富集中带来了公民数量的不断缩减:从公元前480年时的8000人减至公元前418年时大约4000人,接着又在公元前371年减至1200人。到公元前240年左右时,其公民总数降到700人,称得上富裕的大约只有100人。那些资产下降到低于公共食堂贡献门槛的公民被归为“劣等人”:财富不平等侵蚀着公民身份方面的平等主义规范。 [27]
历史证据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对斯巴达大规模军事动员的矫正效应做出保守的估计。这些证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自称珍视平等主义规范的勇士型社会,尽管这些规范在其真实生活中可能从未得到过充分的遵守,尽管代际财富转移带来的不平等结果越来越严重,它们势必会在时间之流中趋于衰落。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本身并未因这一趋势而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地位较低的斯巴达人以及拉科尼亚地区的那些被征服城市中的公民,都在斯巴达方阵中作战,就连农奴也承担着支持军队的职能。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平等主义规范,与从大量依附性的劳动人口中抽取租金相结合,使得针对核心公民的大规模动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仅凭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在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主要是消费和生活方式上的平等,但至少最初还应在资源的总体分配上维持相当大程度的平等,特别是在被征服的领土及被贬为奴的居民被分配给斯巴达的市民时。然而,长远来看,由于缺少任何形式的累进征税和周期性的土地再分配,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主义规范无法遏制日渐拉大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民众的贡献事实上是累退性的,因为加在他们身上的是与个人富足程度无关的固定税收。直到财富集中已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3世纪,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处理。再后来,经由历史上一种典型的矫正途径,即诉诸战争,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见后面的第8章和第12章)。
在史料记载最为完备的城邦,即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似乎更好地起到了遏制资源不平等的作用。现有的史料证据足以使我们在更广泛的军事参与、更充分的公民赋权以及有利于平民而非富人精英的再分配措施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自我强化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大约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追寻这些发展的轨迹。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力日渐充足,雅典的不平等不断加剧。穷人被认为亏欠富人,并且在无力偿付债务的情况下会被贬为奴。雅典当时的一个主要对手,即比邻而立的城邦麦加拉,建立了一种被一份史料严斥为“不受控制的民主”的体制——民粹统治的一个非常早的实例。这个政体确立了一种意在通过牺牲富人利益来惠及穷人的、有追溯力的债务减免制度,即要求债权人偿付贷款利息。政治上的改革促进了全民性军事动员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麦加拉的海军实力大为提升——希腊的战船靠桨来驱动,这意味着划船手的数量是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以至它最终战胜了雅典,并控制了一座双方常年争夺不休的岛屿,即位于两个城邦之间的萨拉米斯岛。这次失败之后,雅典紧接着就实施了一整套的改革,其中包括某种形式的债务取消规定和禁止债务奴役的规定,以及其他一些提升民权的措施。随后,战争的运数很快就发生了转变:雅典人的胜利很可能源自其社会共识和社会协作的改善。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即公元前508年,在对希腊内部的一次领导权之争施加干预的过程中,斯巴达入侵并暂时占领了雅典。在联合起来的城市民兵(其组织包含“17层等级”)的抵抗之下,斯巴达人最终从雅典撤军,由此,大规模动员很快便终结了这次入侵。与这场冲突几乎同时发生的是雅典人口和领土的一次剧烈重构,其结果是雅典被重新划分为一系列选举和军事征募区,其根本意图在于提升社会凝聚力,同时为建立一支统一的公民军队创造条件。这一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就是雅典在与几个主要地方性力量的军事争斗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一旦那些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基本军事和政治制度框架建立起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和政治动员之间就会逐步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环路。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说就是:
当平民处于专制统治的压迫之下时,他们从未在战争中取得过比任何一个邻国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旦抛开了这种桎梏,他们就能向世人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
事实上,除了这一沉重的枷锁之外,希腊的平民还承受着许多小的约束:随着军事任务不断增多,政治参与方面的各种限制逐渐放松。 [28]
随后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更大。在此期间,雅典的海军力量扩充了几倍,到最后雅典成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公元前490年,波斯对雅典的入侵遭到了由8000人组成的革命军的抵抗,这一人数占达到适合参战年龄的男性人口总数的40%。当时,军队统帅和其他高级军官都由公民议会直接选举产生,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临时罢免(“排斥”)不得人心的政治家。公元前480年,在波斯发动另一轮入侵的情况下,雅典人推出了一项法令,意在将数量约为20000人的全部成年男性公民以及寄居雅典的外国人都发动起来,以支持其200艘战舰投入作战。趁打败波斯人之机,雅典很快就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盟系统,由此而来的财力提升使得它有能力进一步扩充海上力量。最终,雅典变成了一个海洋帝国的中心。公元前460年时,雅典军队在希腊和黎凡特地区的活动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军事上的成功又一次带来了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精英群体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以公民议会、代议委员会和人民大法庭为组织基础的民主治理结构进一步得到加强。普罗大众的福利也得到大幅提升:国家为陪审团成员支付薪资的制度得以建立;到公元前440年时,国家大约为20000雅典人所提供的服务支付了酬劳;此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数以千计的人分到了土地。鉴于其海上力量的强弱高度依赖于大规模民众动员的水平(以动用私人奴隶来扩大动员规模),所以二者之间是共存共荣的。
在与斯巴达及其盟国交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的军事动员和军事消耗达到新高。然而,虽然雅典的财力越来越紧张,但在这场战争的后期,下等阶层获得的国家偿付其实是增加了的。海上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一直都至关重要。
这就是平民理应比贵族和富人得到更多的原因所在:正是这些平民在战船划桨,城邦的力量因他们而增强。
战争结束后的尸体清理情况也反映了雅典的军事动员所达到的非同寻常的程度:60000名男性公民中,24000人战死,另外还有20000人死于一场被围攻状态下不断恶化的瘟疫。无论依据何种标准,这肯定算得上一场全面的战争。然而,在人口数量开始恢复之后,雅典人通过重建一支海军恢复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357年时,其战力达到拥有283艘战舰的峰值。大规模动员与内部谈判携手并进的局面再次出现,后者带来了国家补贴的增加:为公民出席议会提供的酬劳提高了6~9倍,同时,陪审团成员比之以前更具雇佣性。为了对公民出席国家节庆活动提供补贴,一项特殊基金得以创立。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公元前323年,雅典人倾尽全力打了一场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战争,动员了所有满40岁的男性公民,同时还动用了240支战舰。大约有1/3的成年男性公民被派遣到海外或在海军中服役。 [29]
这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与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所得被用于补贴雅典战争机器这一情况不同,公元前4世纪的军事活动高度依赖于针对富人的国内征税。与此同时,由于海军是战争动员的重点所在,所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通过再分配手段补贴那些负责载人和划桨的贫苦公民。等到帝国开始衰落之后,雅典人的财政部门主要靠征收各种间接税获益,如通行费和港务费、铸币利润以及包括矿山在内的国有土地租金收入。直接税则征收得很少,仅包括一项加在外来侨民身上的人头税,一项为维持特殊军事开支而向富人征收的财产税,以及一项只加在最富有公民成员身上的作为一种祭祀仪式的献金。虽然这些祭祀献金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用于筹办公共宗教节庆活动和戏剧表演,但其最重要和义务性的用途是装备战舰。在任何特定年份,那些被挑选出来提供献金的人都被要求对某一艘战舰负责,包括负责招募船员(虽然他们会得到国家提供的定额补偿,但仅仅有这种补偿可能是不够的),承担修理费用以及购置设备——他们甚至还可能有义务补偿战船在海上的损失。在精英圈子中,这些义务以及他们因相互攀比而激起的竞争性支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无底洞。这一制度是随时变化着的:公元前5世纪时,海上祭司(通常他们也是所负责的战船上的船长)是从400个最富有的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但到公元前4世纪时,有1200个资产所有者(后来大概只有300个)被要求提供献金。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运作方式下,雅典每个地方都有1%~4%的家庭因此而受累。这种被称作“特瑞希”的献祭仪式在这些家庭之间不断地轮转,每个家庭都不会连续承担两次。 [30]
一次献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雅典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收入的8倍,或者相当于一个典型精英家庭的大部分年收入。即便是富人也不得不以借贷或抵押的方式来筹措祭祀所需的资金。公元前4世纪中叶,祭司阶层的规模达到1200人(最大规模),其每个成员每年平均提供的祭祀献金,大约是最低限度的家庭年收入的3倍,它们被用于维持一支由30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资助公共节庆以及支付财产税。就我们所知的进入祭司阶层所要达到的财富门槛标准而论,履行献祭义务很可能会使得一笔与该标准相当的财富的年收益化为乌有,在把日常生活支出也算在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所做的猜测,雅典400户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相当于贫困家庭年收入的12倍。对这一群体来说,提供祭祀献金,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要将自己收入的1/4以税收形式上缴给国家。尽管相关证据存在严重的不足,但我们仍然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雅典对其富人精英阶层征收了数量可观的所得税。 [31]
除非我们漏掉了有关祭祀献金支出在该阶层内部非均衡分布的历史细节,否则,这一制度就并非总是累进性的,因为无论祭司的实际收入比既定的分界线高多少,国家从中抽取的献金数额都是固定的;最富有的祭司只是被指望先垫付献金,然后再从别人那里收回它们。尽管如此,就其他的公民完全不用缴纳直接税而言,它又是高度累进的。这里有两个关键之处值得强调。一是这一实践主要源于实施大规模(海军)动员所引起的巨大财政需求。选民一方面定期在军队服务,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政治权利的事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必然要由那些最富有的人承担。另一个关键之处更直接地与矫正有关:祭祀献金制度势必会减少,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阻碍雅典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雅典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非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境下,祭祀献金制度起到了遏制不平等的作用,如若不然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拉大。因此,被现代人视为笑谈的抱怨并非只是夸张:
我们何时才能摆脱祭祀献金和战船捐献的重负获得一点喘息之机?
不管怎样,那种认为财政干预抑制了不平等的观点,与我们有把握说清的那个时候雅典的财富分配状况是相吻合的。现代学者做出的两个独立的估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比较平等的土地分配图景:7.5%~9%的雅典人拥有30%~40%的土地,只有20%~30%的人根本没有土地。作为“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足够打一场全副武装的方阵战)所占有的土地份额是35%~45%。这意味着,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其土地所有权基尼系数达到0.38或0.39,是比较低的,但它与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大规模财产这一点是吻合的。然而,这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非土地资产方面存在着更不平等的分配。 [32]
一些大胆的历史学家走得更远,有人估计当时雅典人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38,还有人估计雅典公民阶层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也就是说,前1%和10%的财富精英分别占总财富中30%和60%——但它们都是不可检验的猜测。我们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所做的估计表明,按照前工业化时期的标准,雅典人在某些行业中的真实工资水平是很高的:它们是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数倍,与现代早期时荷兰人的最低收入相当。这个观察,再加上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高度的土地集中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大规模财富,都意味着物质资源在雅典公民阶层中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最后,如果说我们对雅典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经济规模所做的估计不是很离谱的话,那将意味着,在公元前430年以及前330年时,雅典的公共支出大约占其GDP的15%。 [33]
另外,即便大规模战争是导致财政扩张的首要因素,我们仍然必须将民用性开支考虑在内并赋予其相当的权重: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的那些年份里,一半以上的公共支出都用在了非军事性的活动上,如对政治参与和陪审活动提供补贴、节庆支出、提供福利以及公共建设支出,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这些活动而受益。这一点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引人注目:对这样一个前现代社会来说,其国家占有GDP的份额是很高的;民用支出占总开支的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在帝国的收入枯竭之后,累进性征税最终取代掠夺性的献祭仪式成为公共开支的来源。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民主,累进性的征税,很大一部分GDP被国家占有,大量的民用支出,受到约束的不平等这些事物聚集在一起,赋予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雅典一幅特别怪异的、早熟的“现代”样貌。
对雅典来说确定无疑的事情,并不一定也同等地适用于其他1000多个城邦,这些城邦共同构成了成熟时期的古希腊城邦文化,但也没有明显的途径去证实这一点。虽然在实施大规模军事动员方面,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形,但其他的城邦也被认为建立了军事守备力量,这势必会造成其人口资源紧张。我们发现,那个时候民主式统治变得越发普遍,而且战争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公元前430—前330年的这一个世纪,几乎是战争不断,参与其中的既有地面力量也有海军,并且,虽然雇佣军的作用在逐步增强,但从公民中征募士兵通常还是很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提供了有关当时物质不平等状况的或许是最具普遍性的证据。房屋的大小——私人住宅普遍地接近中位值:公元前300年时,在大小上处于第75百分位的房屋仅比处于第25百分位的房屋大1/4左右。公元前4世纪时,在奥林托斯这座公认由人为规划建造而成的城市里,有关房屋大小的基尼系数仅为微不足道的0.14。 [34]
因此,大量的历史记录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古希腊城邦文明在不断蔓延扩张过程中维持着相对温和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得益于广泛存在的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文化,同时也受到了公民权利制度以及加速推进的民主化的影响。为了防止被其他城邦吞并,这种文化还禁止人们跨越自己所在城邦的界线去寻求资本积累。早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的远古时期,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财富积累行为所遭遇的政治和社会阻力就已经很大了,这为古典时期政治分裂和城邦之间长期相互敌视关系的出现做了铺垫。在这方面,雅典帝国算得上一个打破常规的例外。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希腊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帝国系统吞并和支配,其平等主义规范逐渐式微,与此同时财富积累也迎来了一次崭新的历史机遇。 [35]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战争。它们通常是发生在查尔斯·蒂利所谓的“暴力专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归根结底,主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之间为控制人民、土地及其他资源而展开的角逐——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是“国王之间的比赛”。在那些只有一方遭受严重破坏的战争中,掠夺和征服可能会在加剧征服者之间不平等的同时,降低受损或战败方之间的不平等:战胜方的领袖往往大获其利(与其追随者相比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是与普罗大众相比了),战败方的领袖通常会损失惨重甚或丧命。战争的性质越“古老”,这条原则往往体现得越充分。对被征服者的掠夺可以远溯到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正如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在挽歌中唱的那样:
哎呀,老天,我算是彻底毁了呀!
那个敌人踩着他的靴子闯进了我的卧室啊!
那个敌人脏兮兮的手向我伸过来了啊!
那个敌人剥掉了我的袍子,穿在了他妻子身上啊!
那个敌人扯下了我的一串宝石,挂在了他孩子身上啊!
我非得把他的房子踏平不可。 [36]
然而,虽然许多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但富人们失去的更多——相应地,其战胜方中的那些伙伴得到的也更多。让我们到美索不达米亚逗留一会儿,看看那里继苏美尔人的灿烂文化陨落几千年之后出现的新亚述王国吧。当亚述王国的统治者四处洗劫和掠夺城市并屠宰和驱逐城市的居民时,亚述的王族却令人厌恶地频频撰文来夸耀他们的赫赫战功。鉴于他们往往只是笼统地描述劫掠的过程,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遭到了洗劫。但每每碰到有具体描述的文本时,它们都表明敌方的精英阶层是被专门挑选出来的掠夺对象。公元前9世纪,当亚述统治者撒缦以色三世打败楠瑞的国王马尔杜克—莫达米克时,他“洗劫了他的王宫,掳走了他的上帝(神像)、财产、物品、宫中女眷,以及不计其数的挣脱缰绳的马匹。”
在有关撒缦以色三世的其他铭文中,其掠夺王宫财产的场面反复被提及,其中一篇铭文甚至告诉我们“许多黄金做的门”被敲碎并运走。劫掠之后,敌方统治者连同他们的家族,以及宫廷人员和女眷这类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人,都会遭到放逐。亚述的其他国王据说还会把战利品分给其他精英受益者。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失即是另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得。如果战争的一方总是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么这些胜利者精英就会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源财富,同时把被征服者甩在身后,这一过程会通过拉长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顶点之后的尾巴,抬高整体上的基尼系数。正如我在最初两章中所论证的,大的附庸国越多,国家越容易在统治阶级的最顶层中形成不成比例的物质资源集中。 [37]
传统战争的“零和”特征,在1066年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征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土地财富方面看,当时英格兰的贵族包括几个极其富有的伯爵以及几千个小领主和地主。罗马最初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随后便遭遇了长达数年的反抗,在此情况下,征服者威廉先是试图拉拢这个集团,但接着推行了全面的征用政策。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土地转移,使得国王占有的土地份额大为提升,同时足足有一半的土地最终落到大约200个贵族的手中,这其中又有半数为新国王的10个亲密盟友所占有。尽管新国王的亲密盟友享有特权,但已不像此前穷奢极欲的伯爵那般富有了,其他的那些男爵要比以前的小领主富有得多。这种强力再分配的影响深入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各个等级:到1086年英国发布土地勘察报告时,那些能被明确地认作英国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就面积而论占6%,就价值而论仅占4%;尽管他们的实际份额可能比这更高,但毫无疑问的是罗马贵族已接管了大部分的土地。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小领主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到别处以当雇佣兵为生。时移世易,随着王族的土地不断减少,以及贵族们不断将土地打赏给依附于他们的骑士,这一早期出现的土地集中过程最终被大幅度地逆转,从而再造出了一个整体规模更大但单个来看富有程度相对更低的精英阶层。然而,封建关系使得任何有关这一时期土地财产分配情况的观察变得更加复杂。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情况甚至更难以确定,但一般说来,看起来罗马人的征服最初确实带来了土地收入在一个比此前小得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更大程度的集中,只不过这个阶级随后便逐渐趋于解体。 [38]
在这种传统的战争和征服过程中,矫正或许主要是发生在战败方的各个领导者之间,例如,西亚的统治者就是被愤怒的阿舒尔或哈罗德国王手下的那些领主拉下马的。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城提供了一个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1478—1546年,在瘟疫已经消退且周边的城市共同体正出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普拉托的财富基尼系数(依据财富税缴纳记录推算得到)反而从0.624降到0.575。1512年时,普拉托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血腥洗劫,据说导致数千人丧生以及长达三周肆无忌惮的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成了劫掠者大肆捞取赏金的主要对象。在第11章结束时,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德国奥格斯堡市的例子,它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了敌方和瘟疫的双重重创,因此最后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的大幅缩减。尽管瘟疫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引发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因战争而来的资本价值损失,以及富人承受的非同寻常的负担。 [39]
虽然我们可以从战争编年史中搜罗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这样做意义不大,因为一般性的原则已经很清楚了,尽管我们无法对之做出可靠的测度。在传统战争中,矫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战争带来的掠夺或破坏程度,胜利者或征服者的最终目标,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界定我们的分析单位。如果我们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胜利者与失败者视为分离的实体,就可能会认为矫正主要发生在后者之间。如果战争带来了彻底的征服,而且胜利一方的成员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从而以一个新的精英阶层部分或完全替换掉以前那个旧的精英阶层,那么,总体上的不平等就不一定会受到大的影响;如果原来的精英阶层及其所拥有的财产最终被并入帝国系统,那就会创造出一个规模更大并且不平等关系更为广泛的政体。然而,这种粗糙的分类法肯定会造成对更复杂的真实情况的过分简化。无论是军事精英还是社会精英,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对那些无法清楚地区分胜者和败者的战争来说,这种方法尤其成问题。举两个例子就够了。1807—1814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后者的领土打的那场半岛战争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实际工资水平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并且在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激增。相反,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实际工资水平以及相对于地租而言的名义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上涨,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也更低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发生的那场毁灭性战争以及持续的国内动荡,看起来也造成了地租与工资之比的大幅下降。 [40]
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内战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的?现代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相反的问题——不平等是否是导致爆发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这第二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一方面,总体的(或者“垂直的”)不平等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是正相关的(尽管依据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那些低质量数据,任何可靠的具体结论都可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能够被证明对内战有促进作用。最近出现的一些研究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项调查研究指出,人体重量不平等——作为资源不平等的表现与内战存在正向关联,并且,这项研究的样本空间十分广泛,甚至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此外,根据另一项研究,爆发内战的概率随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不过后者非常高的情况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弱小的精英人士的广泛存在会使得镇压动乱变得更容易,所以前者反而会下降。因此,我们只能说有关这个问题的巨大复杂性才刚刚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41]
相比之下,内战对不平等的影响问题几乎还未引起多少注意。一项以1960—2004年128个国家为样本的先驱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在内战结束后的前5年时间里。平均而言,这些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在内战期间会上升1.6个百分点,在随后10年的复苏期会上升2.1个百分点,并且,若能维持和平的话,会在战争结束5年后达到峰值。好几种原因促成这种趋势。鉴于内战会使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它们的价值会上升,与此同时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会下降。更具体地说,在有着大面积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可能会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并因为被排除在商业交易之外而收入受损,这些损失会将农民逼入生存的边缘。与此同时,战争投机商则会趁着安全下降和国力衰微之机牟取暴利。商业投机只会让很少一部分人受益,故而当国家的征税能力下降时资源集中就会出现。这种紧缩连同军费开支增加,带来社会性支出较少的情况,这反过来又会损害穷人的利益。再分配政策以及公共教育和健康支出备受挤压,并且冲突持续得越久,这种负面效应就越强。 [42]
这些问题在战争之外仍然存在,我们发现在紧接内战之后的几年里,基尼系数甚至更高了。在那一时期,胜利者会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因为“个人与家族关系决定着财产以及获益机会的分配”。这一特征是内战与前现代传统战争的共同之处:胜方的领导者得利,不平等加剧。19世纪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点:19世纪3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战时期的土地充公政策最终带来了大宗地产的出现和不平等的加剧。 [43]
几乎所有相关的观察都源自传统社会或者发展中国家。在更发达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内战是很少见的。另外,在某些内战与大矫正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案例中,如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颠覆性的变革而非内战本身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美国内战看成一场类似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本章前面部分已做了描述。这使得我们只剩下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可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不同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这场内战的胜利一方并未追求一种再分配议程,其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革命性的。冲突期间,那些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地区施行了集体化政策,但非常短命。1939年之后,弗朗哥派实施的自给自足政策导致了经济上的停滞。内战引发的一系列冲击以及随后的经济管理不善,带来了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段时期只有最顶层群体(最富的0.01%群体)收入份额的计算数据,它在1935—1961年下降了60%。这一趋势与总体上的收入基尼系数变化情况相冲突,后者在内战和“二战”期间比较稳定,但在1947—1958年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图6.2)。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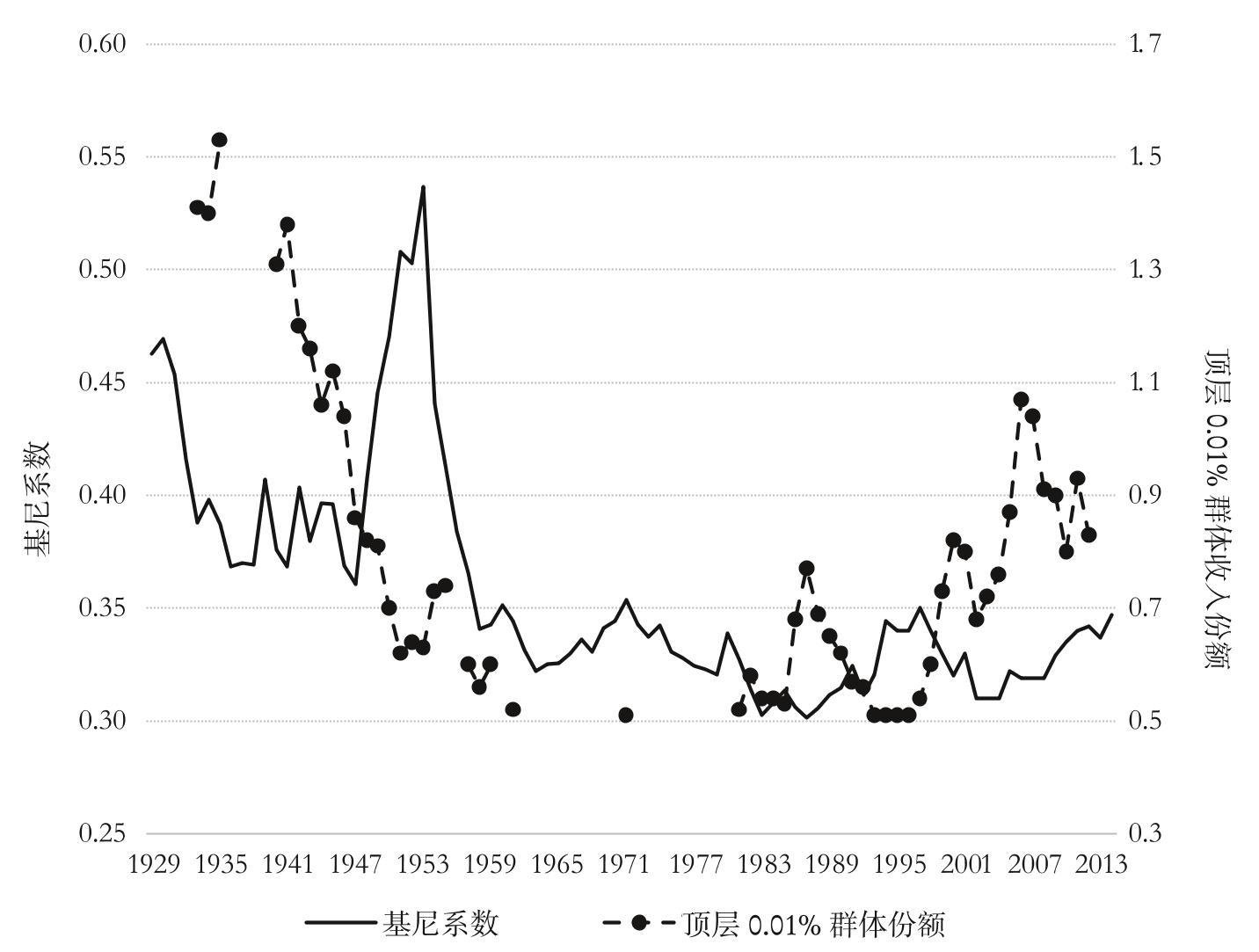
图6.2 西班牙的收入基尼系数及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1929—2014年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工资收入基尼系数在1935—1945年出现了幅度约为1/3的显著下降。就我们所知,迄今还未见有人对这些结果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针对以下现象提出了几种假说:资本收益下降(这会压低顶层收入份额)引发的竞争效应、弗朗哥统治下的再乡村化运动带来的工资收入缩减(这会削减总体收入不平等)、自给自足政策下财产尤其是土地收益的上升(这抵消了那些会抬高总体基尼系数的收入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均实际GDP出现零增长的1930—1952年,贫困人口比重在此期间也大致增加了一倍。不平等在西班牙的变化过程十分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就顶层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下降而言,它们有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与卷入“二战”中的其他国家及许多中立国不同,西班牙并未实行累进性的征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未下降。我同意普拉多斯·埃斯科苏拉的一个说法,即:“把握住西班牙(内战对其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它们的社会凝聚力因世界大战而增进)之间的区别,对理解战后时期的事态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二者赖以形成各自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驱动力是相同的,即受政府政策调节的暴力冲击。 [45]
我将再次回到遥远的过去,通过考察一个混合型的案例来结束我的研究,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80—30年代之间、并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之所以称其为混合型的,是因为它们是罗马社会内部的冲突;它们因流亡精英群体的竞争而起,但具体发展以前面曾提及的大规模军事动员文化为背景,从而表现出国与国之间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关键特征。罗马人在军事动员率上的最高历史纪录就出现在这一内乱时期。同时出现在这场战争中的精英群体内讧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中,那些爆发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和公元前1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血腥的冲突彻底摧毁了罗马的统治阶级。政敌遭到排斥,统治阶级公开宣布任何想杀死政敌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一份赏赐,他们的财产也会被胜利方没收充公。在公元前83—前81年的内战中,据说有105位参议员遭到了杀害,当时参议员的总席位只有300个左右;公元前43年,300位参议员(总数是600个)以及2000个爵士(他们是罗马社会中的第二大精英阶层)以同样的方式丧命,虽然我们仅能指认出其中的120位。这两段插曲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不平等的进程。第一轮没收充公是由寡头反动势力的支持者操控的,他们允许占据优势地位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过程中抢购没收得来的财产而获利。这很可能带来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特别是在内战前夕精英阶层出现大幅减员的情况下:从公元前90—前80年的10年间,据说至少有291位参议员丧命于暴力。继承者数目减少带来的很可能是精英财产的联合而非分散化。从当地各个社群没收得来的土地原本是要给退伍老兵的,但往往最后还是流入了市场,由此而来的交易也起到了促进财产集中的作用。公元前43年和前42年发生的没收充公则有所不同,它们的起因不是为了报仇,而在于从军事上做好抵御那些流亡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内政敌的准备,财政需求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既然如此,没收充公得来的财产就不太可能用于犒赏同盟者,而主要是为了兑现为组建一支庞大的市民军队所承诺的高额补偿金。派系领袖的那些亲密盟友一直到公元前30年的冲突尘埃落定后才获得了奖赏,并且奖赏的具体方式是以牺牲旧贵族利益为代价培植“新贵族”。 [46]
士兵在这最后一轮内战中获得的高额补贴,兴许起到了显著的再分配作用。内战爆发之前,罗马士兵只能得到比较适中的补偿。在早期抵御外敌的战役中风行起来的军阀做派最终推高了补偿的额度:它们起初是很低的,但到公元前69年时一下子就涨到年最低薪酬的7倍,公元前61年时更是达到年最低薪酬的13倍。公元前40年的内战带来了士兵补贴金进一步的大幅上涨,到公元前46年时已22倍于新调高后的最低年薪(或者42倍于旧的最低年薪)。4年之后,这项开支很快又创下新高,因为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后勤人员也得到了获得同等补贴的许诺。总之,我们估计,公元前69—前29年,为收买军心和犒赏军队,一笔至少10倍于国家常规收入,或相当于当时罗马年GDP总量的巨额资金,最终被转移到士兵的手中(几乎所有的支付都发生在公元前49—前29年)。领到补贴的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大约占罗马公民总量的1/3。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通货膨胀,所以这很可能带来了非精英群体实际收入的大幅上涨。罗马社会内部的分配效应在意大利中心地区的表现如何,就更加晦暗不明了。这笔巨款中有大部分都是从外部各省搜刮来的。但也有例外:公元前43年时,除了施行上面已提到的大规模没收充公,富人还被要求上缴一年的不动产收益以及2%的财富税。后来又增设了多项富人缴税义务。财政课税事实上以累进的方式进行,且征得的税收供再分配之用,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47]
不过,这终归只是一次性的偶发现象。公元前30年罗马恢复和平并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体制之后,依靠征税汲取财政收益重新成为常态。国家所支配的财政收入,仅仅只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几年里,被暂时性地用于提升一般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长远来看,随后几个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稳定局面,无疑有助于促进高水平的财富集中。
本书的这一部分已经带领我们穿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军事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只有几种类型的战争削弱了另一种同样普遍的人类现象——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无论是对胜利者还是对失败者来说,现代的大规模动员战争都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矫正手段。每当战争的影响渗透到整个社会,资产就会贬值,富人就要为之付出某个公平的份额,战争不仅能够“夺人性命和摧毁财物”,还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二战”时,长期推行的战争驱动性政策,使得这种影响不仅见于战争当时,而且还见于战争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公民所经历的长达一代人甚至更久的不平等程度下降,最终要归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局性暴力冲突。类似的物质不平等缩减也出现在了“一战”期间及之后。这种特殊风格的战争在更早的时候鲜有先例,即便有通常也与矫正无甚关系。在美国内战中,导致南方财富被毁的不是战争动员本身,而是战败和被占领。正如中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依据有关大规模战争远古先例的历史证据所得出的,是模糊不清甚或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斯巴达这个勇士型的城邦,资源分配从早期无疑是平等的状态逐渐演变为一种失衡的状态。古代的雅典,或许是前现代时期民众广泛参与军事的一个最佳案例。正如20世纪的某些时期一样,雅典人共同的战争动员经历看起来强化了他们的民主制度,而这反过来为施行限制不平等上升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鉴于总体发展趋势截然不同且古代的证据资料有限,我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类比。虽然如此,古代雅典的经历却表明,只要各种制度安排搭配得当,即便是在完全的前现代环境下,一种崇尚军事上大规模动员的文化也能发挥出作为矫正机制的作用。 [48]
那种范围更为有限的战争广泛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逻辑一致的规律性结果。以掠夺和征服为主题的传统战争,普遍而言会使精英阶层获益,从而加剧不平等。每当战败一方被归并到一个更大的政体中时,情况尤其如此,而上层社会阶梯会因为这个归并过程而出现更多的财富或权力层级。内战很少会起到矫正的作用——即便真的起到了这种作用,那也是部分地(正如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班牙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那样)或短暂地(或许像古代的罗马那样)。唯一能够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内战,是那种由颠覆政权的激进统治者发动的革命,他们一心想着全面地征用和再分配,且不惜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一过程,正是我们马上要论及的暴力矫正的第二个骑士。
[1] Fig.6.1 from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177 fig.7.1.
[2] 单有大规模军队并不一定能满足这一标准:例如,中国在1850年时要想达到这个2%的门槛线,就得有近900万人在军队服役。据我们所知,即便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也未曾发生:见本书第8章。
[3] Bank, Stark, and Thorndike 2008: 23–47 on Civil War, esp.31–34, 41–42.
[4] Turchin 2016a: 83 table 4.4, 139, 161.For the evidence of the census data, see herein, n.7 and also Soltow 1975: 103.Between 1860 and 1870, the estimated Gini coefficient of property income rose from 0.757 to 0.767, and the top 1 percent share from 25 percent to 26.5 percent—changes that are well within likely margins of error: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122 table 5–8.Income Ginis went up 6.1 points in New England, 3.1 points in the Middle Atlantic states, 6.7 points in the Eastern Northern Central states, and 5.9 points in the Western Northern Central states, whereas the corresponding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s grew from 7 percent, 9.1 percent, 7 percent, and 6.9 percent to 10.4 percent, 9.2 percent, 9.1 percent, and 9.7 percent: 116 table 5–7A, 154 table 6–4A.
[5] Slaves as wealth: Wright 2006: 60 table 2.4, with 59 table 2.3(在南方的私人财富总量中,农用耕地和建筑物所占的比例是36.7 %)。Cf.also Piketty 2014: 160–161 figs.4.10–11 for earlier decades.Ginis: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38 table 2–4, 116 table 5–7; and cf.also 115 table 5–6 for 1850.Slaveownership: Gray 1933: 530 with Soltow 1975: 134 table 5.3.
[6]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Joshua Rosenbloom and Brandon Dupont, who very generously computed these results for me from IPUMS-USA, https://usa.ipums.org/usa/.For the nature of these data, see Rosenbloom and Stutes 2008: 147–148.
[7] 根据IPUMS-USA提供的数据,整个南方的财富基尼系数在1860年时为0.8,1870年时为0.74。更早的研究估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这10年所发生的财富矫正更温和。Soltow 1975: 103 estimates wealth Ginis of 0.845 for free Southerners in 1860 and 0.818 for Southern whites in 1870.Jaworski 2009: 3, 30 table 3, 31, drawing on 6,818 individuals from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studied in both 1860 and 1870, computes a decline of the wealth Gini from 0.81 to 0.75 in the Atlantic South caused by losses at the top and a rise from 0.79 to 0.82 in the South Central region caused by rapid wealth accumulation by white-collar workers.Rosenbloom and Dupont 2015 analyze wealth mobility in that decade and find considerable turnover at the top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Property income: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122 table 5–8.Table 2.4: 116 table 5–7, 154 table 6–4A (all Ginis rounded to two digits behind the decimal point).For a comparison of free households in 1860 and white households in 1870, see 116 table 5–7, 155 table 6–4B, for top income share reductions by 32 percent, 23 percent, and 49 percent of 1860 levels and Gini reductions by 4, 3, and 8 points.
[8] 美国和日本的顶层收入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的快速恢复,看起来只能算是个别例外情况。
[9] Quoted from Schütte 2015: 72.
[10] Clausewitz 1976: 592.
[11] 参见本书第8章。
[12] 为了和本书总体关注的焦点保持一致,在这里我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农耕社会,而不考虑其他类型的国家或社会,例如那些卷入了零星或季节性战争且维持着很高参与率的小型社会,或者像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后继者所领导的那种主要依靠成年男性的游牧社会。
[13] Kuhn 2009: 50 (Song); Roy 2016: ch.3 (Mughals); Rankov 2007: 37–58 (higher figures for late antiquity are not credible: Elton 2007: 284–285); Murphey 1999: 35–49 (Ottomans).
[14] Hsu 1965: 39 table 4, 89; Li 2013: 167–175, 196.当时的政治话语表现出了对民众疾苦更大程度的关注,国家也试图减轻百姓的贫困和不幸,“惠民”“爱民”这类语汇风行一时:Pines 2009: 199–203。
[15] Li 2013: 191–194; Lewis 1990: 61–64; Lewis 1999: 607–608, 612.
[16] Li 2013: 197; Lewis 1990: 15–96, esp.64 (quote).
[17] Campaigns: Li 2013: 187–188; Lewis 1999: 628–629; Lewis 1999: 625–628 (army sizes); Li 2013: 199; Bodde 1986: 99–100 (fatalities); Li 2013: 194 (Henei).在500万人口的国家征召10万名士兵,已经达到了上面提及的2%的门槛线标准。
[18] Lewis 2007: 44–45; Hsu 1965: 112–116; Sadao 1986: 556; Lewis 2007: 49–50.Quote from Lewis 2007: 50.
[19] Falkenhausen 2006: 370–399, esp.391, and 412, invoking egalitarianism as well as militarization.This contrasts rather awkwardly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such weaponry from Qin graves, possibly for utilitarian reasons (413).
[20] As for higher Qin taxes, we cannot be sure whether this was true or merely hostile propaganda:Scheidel 2015b: 178 n.106.
[21] Scheidel 2008 surveys the debate about the number of Roman citizens.For mobilization rates, see esp.Hopkins 1978: 31–35; Scheidel 2008: 38–41.Lo Cascio 2001 argues for a larger base population and lower participation.
[22] Livy 24.11.7–8, with Rosenstein 2008: 5–6.For Athens, see hereafter.
[01] 古南方地区,指美国南部地区最初作为英国殖民地而出现的13个州,西方学者通常用它来指称一种农耕式的、前市民化的战争经济与社会形态。——译者注
[23] Hansen 2006b: 28–29, 32 (population); Ober 2015a: 34 fig.2.3 (territories); Hansen and Nielsen 2004; Hansen 2006a (nature of the polis).
[24] Ober 2015a: 128–137, esp.128–130 (quote: 130), 131 (quotes), 131–132, 135–136.
[25] 很多学者假定了一种紧密的(因果)联系,然而其他学者对此持有疑虑。Van Wees 2004: 79 and Pritchard 2010: 56 are among the most critical voices.See van Wees 2004:166–197 for the mixed character of the early phalanx.Rights: Ober 2015a: 153.
[26] Plutarch, Lycurgus 8.1 (transl.by Richard J.A.Talbert).
[27] Hodkinson 2000.Concentration: 399–445, esp.399, 437.For the disequalizing effect of hereditary resources, see herein, chapter 1, pp.37–38.
[28] See Scheidel 2005b: 4–9 for a fuller account of this whole sequence of developments.Pritchard 2010: 56–59 urges restraint.Quote: Herodotus 5.78.
[29] Quote: Old Oligarch 1.2, quoted from van Wees 2004: 82–83.也可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4a:“这些海上暴徒基于雅典的海上实力在萨拉米斯取得胜利,并由此造就了雅典的霸权地位之时,也是民主制进一步得到加强之时。” Note that the undeniably polemical character of this and similar statements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them untrue,as implied by Pritchard 2010: 57.Hansen 1988: 27 (Athenian casualties); Hansen 1985: 43(Lamian War).
[30] Ober 2015b: 508–512; van Wees 2004: 209–210, 216–217.
[31] Burden: see Pyzyk forthcoming, with Ober 2015b: 502.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最富有的(大约)1%群体的所得就非常少了,可能只占全部私人所得的5%~8%左右。如果构建一个将该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翻番的模型,那将意味着该群体税收负担会降低到原来的1/8(同时会使他们的收入份额翻番,变为13%左右) ,但同时也意味着,紧随其后的800个次等富有的家庭承担了更重的税收负担: Ober 2015b: 502–503; 2016: 10(doubled elite income).For the nature of Athenian wealth, see Davies 1971; 1981.Income taxation: this disregards the additional effect of occasional emergency property tax levies well beyond the mean assumed in my calculations: see Thucydides 3.19.1 for a charge in 428 BCE that was equivalent to the annual cost of outfitting 300 warships.。
[32] Quote: Theophrastus, Characters 26.6, quoted from van Wees 2004: 210.Land Ginis:Scheidel 2006: 45–46, summarizing Osborne 1992: 23–24; Foxhall 1992: 157–158; Morris 1994: 362 n.53; 2000: 141– 142.See now also Ober 2015a: 91.
[33] Income and wealth Ginis: Ober 2016: 8 (and cf.2015a: 91–93); Kron 2011; 2014: 131.Wealth inequality would have been much higher when resident aliens and especially slaves are included, as noted by Ober 2015a: 343 n.45.Real wages: Scheidel 2010: 441–442,453, 455–456; Ober 2015a: 96 table 4.7.Foxhall 2002 emphasizes the gap between radical political egalitarianism and more limited resource egalitarianism.Public spending: Ober 2015b: 499 table 16.1, 504.
[34] Morris 2004: 722; Kron 2014: 129 table 2.
[35] 正如现代时期的情况一样,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民主制度本身有助于遏制不平等:参见本书第12章。借助现有的有关雅典历史的简要研究可以判断,大规模军事动员和民主化相互联系的方式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形。Lack of consolidation: Foxhall 2002: 215.Note also Aristotle’s unhelpfully vague allusion to ancient laws in “many places” that had capped land acquisition (Politics 1319a).
[36] Tilly 2003: 34–41; Toynbee 1946: 287.Gat 2006 and Morris 2014 surve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rfare across history.Lament quoted by Morris 2014: 86.
[37] Yamada 2000: 226–236, esp.227 (quote), 234, 260; Oded 1979: 78–79, and herein, chapter 1,p.61 (distribution).
[38] Nobility: Thomas 2008: 67–71, esp.68; Morris 2012: 320–321.New distribution:Thomas 2008: 48–49, based on Thomas 2003; Thomas 2008: 69.土地所有权空间分布方面的变化(更紧凑的诺曼庄园最终取代了英国人原本分散化的资产) 没有对这一过程造成什么影响,而后来出现的长子继承权制度有助于维持已有的财产分配格局:Thomas 2008: 69–70, 102。
[39] Prato: Guasti 1880; Alfani and Ammannati 2014: 19–20.Augsburg: herein, chapter 11, pp.335–341.
[40] A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13: 6 fig.3, 9 fig.3, 21 fig.8, and herein, chapter 3,p.99 fig.3.3 (Spain); Arroyo Abad 2013: 48–49 (Venezuela).
[41] Overall inequality: Fearon and Laitin 2003; 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Intergroup inequality:Ostby 2008, Cederman, Weidmann, and Skrede 2011.Height inequality: Baten and Mumme 2013.Land inequality: Thomson 2015.
[42] Bircan, Brück, and Vothknecht 2010, esp.4–7, 14, 27.The section title quotes a Hutu killer reminiscing about the genocide near the end of the Rwandan civil war of 1990–1994:Hatzfeld 2005: 82.Perpetrators’ narratives reference some of the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study: “we can’t say we missed the fields....Many suddenly grew rich....We were not taxed by the commissioners” (63, 82–83).
[43] Quote: Bircan, Bruck, and Vothknecht 2010: 7.1830s: Powelson 1988: 109.
[44] On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see, e.g., Holtermann 2012.Spain: Alvaredo and Saez 2010,esp.493–494; WWID.Fig.6.2 reproduced from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8: 302 fig.6.
[45]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8: 294 fig.2 (wage Gini); 288 table 1 (GDP 1930–1952), 309 fig.9(poverty 1935–1950); 301 (quote).
[46] Shatzman 1975: 37–44.
[47] Scheidel 2007: 329–333.
[48] Quote in the text: I owe this apt characterization of military activity to former Arkansas Governor Mike Huckabee, offered in the firs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primary debate on August 6, 2015.
如果说国与国的冲突能降低不平等,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史中,内战并没有造成明确的影响,然而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往往是拉大了原有的差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内部冲突不仅仅是派系之间的对抗,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重组?如此雄心勃勃的企图并不多见。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性的群众起义都是出于消除现实中的不公的理由,然而很少能够达成所愿。成功夺取了权力并且使收入和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运动,只出现在近期。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甚为相似,行动的强度是个关键指标。尽管大多数的战争并没有带来平等化的结果,但是一次军事化的群众动员能打乱旧的秩序。在各种起义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进行了类似活动的全面动员,才能带来强烈的矫正。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隐喻,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同为强大的世界末日骑士,它们扫除既得利益,重组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暴力的程度最为关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大多数的平等化革命同样是有史以来所有内部变革中最为血腥的。我对起义和革命的比较研究证明,大规模的暴力是矫正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采取了和前面相同的方法,沿着时间轴进行追溯。最相关的证据还是来自20世纪,如本章所述,一些大型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了收入和财富急剧分散。在下一章,我将转向一些先例,比如最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我们还考察了在前现代社会,用武力改变内部环境的一些行动(比如农民起义)带来的影响。和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我们发现了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近发生的革命,才被证明强大到能影响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在第5章我们已经看到,灾难性的“一战”,是一次调动了前所未见的人力和物力的大屠杀,然而它压缩了主要参战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同的国家,其影响的程度和时机也不相同。在德国,顶层的收入份额在战时上涨,战败后却下降了;在法国,只有战后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在英国,战时和战后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在美国,战时出现下降,然而很快出现强烈的反弹。尤为可惜的是,一些受战争重度影响的国家,比如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没有发布可供比较的数据。“二战”则与之不同,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国造成了强烈而明确的矫正后果,这次“大战”的相关记录有些复杂并且部分未知。 [1]
“一战”之后的俄国,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最为剧烈的下降。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与其说是因为卷入战争——由于战时的混乱或者战后的财政崩溃,还不如说是因为产生于战争残骸中的内部革命带来了矫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帝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参与者之一:它动用了大约1200万名士兵,其中近200万人战死。另外有500万士兵受伤,以及250万被俘虏或者失踪。而且,据估计还有100万的平民死亡。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1914—1917年的战争期间,俄国的不平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减:税制高度累退,严重依赖间接税;直到战争结束,个人所得税和战争收益都没能脱离谷底;国债方案只取得部分成功,大部分的赤字都要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加速型通货膨胀,尤其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时期,并不只是损害了富人的利益。 [2]
无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和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罢工以及几个月后终结了中央政权的对抗行动造成的后果相比,一定会显得黯然失色。那一年出现的巨大经济衰退激起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地主的房屋被接管,罢工工人控制了大量工厂。在1917年11月的6日和7日,以布尔什维克武装组织接管首都为标志,起义达到了高潮。11月,圣彼得堡的冬宫革命风暴发生后的第二天,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由列宁本人撰写的《土地法令》。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项法令以极端的方式横扫一切。它直接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立法来赢得农民的支持。之后,农民夺取和分配贵族和国家的土地,从那一年的夏季开始,一直都在推进。然而用专业术语来讲,这项法令更高的目标是摧毁土地私有制: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此废除,并且不会得到补偿……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被永久废除。土地不得买卖和出租,否则将被没收……土地的使用权被赋予所有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公民,并且不分性别和国别……禁止雇工……须按照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劳动或者食物标准单位的基础上,把土地分配给使用者。 [3]
在当时,这些措施仅仅针对精英阶层——比如大地主、皇族还有教会的土地所有权。普通农民(和哥萨克人)的土地并没有成为没收的对象。征收和分配工作由当地的委员会负责。随后的法令又把所有的银行国有化,把工厂交由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控制,并且没收了私人的银行账户。从经济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家属有大约50万人被消灭了,与此同时,被消灭的还有大约12.5万人的顶层资产阶级。这些“过去的人”中的很多人,因为是被人熟知的精英而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移民国外。激烈的去城市化运动有利于矫正不平等,因此1917—1920年,在财富和收入的两大集聚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口数量下降了一半以上。在1919年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共产党的支持者普拉夫达写道:
时髦的贵妇,高档餐馆,私人豪宅,漂亮的大门,不实的报纸,这些腐败的“黄金生活”都到哪里去了?全部被一扫而空了。
列宁发动的“消灭富人的战争”,已经获胜。 [4]
在这个主要人口仍然在土地上劳作的社会,仅仅由布尔什维克首发的这个《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巨大的矫正力量,并且通过其他的没收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1919年,农民获得了97%的耕地。然而从一开始,新政权就认为仅有这些转移措施还不够,他们担心平等的分配只会“创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并且既不能保证平等,也不能防止分化”。的确,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彻底和永久的矫正。1918年2月,又一个主要的土地法令被用来推动集体化:
在决定授予土地的方式和顺序时,优先选择农业合作社而不是个人。 [5]
在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极为严重地依赖于公开的强制。
强力干预保证了平等,但是也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农民生产不积极,他们销毁牲畜和生产工具以防止被征收,耕地数量和产量大幅度低于革命前的水平。为了应对生产不足,政府推动自愿性质的集体化,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921年,也只有不足1%的俄国人口在集体农场工作。实现全面的平等代价高昂:1912—1922年,没有马或者只有1匹马的农户的比例从64%上升到86%,拥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则从14%下降到3%。整体上农民变得更加平等,然而也变得更加贫困。通货膨胀愈加猖獗:在1921年,物价大约是1914年的17000倍。物物交易逐渐替代了货币交易,黑市也兴旺起来。 [6]
由于产出急剧下降,再加上几百万人在内战中死亡,1921年出现了暂时性的转折——新经济政策推出。市场恢复运行,农民可以用实物交税,还可以销售和消费多余的粮食。土地租赁和雇工也再次被允许。自由化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成效,1922—1927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半。这些政策使一部分人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商品交换,造成生产者再次分化。富农人口出现了非常温和的增长,从占农民总人口的5%上升到7%。然而这些人还远远谈不上富裕,也就是平均一家两匹马、两头牛,拥有一些可用于交易的粮食。总体而言,早期富农的财产和土地被分配给无地的生产者,平衡了收入分配,导致“农民中农化”。企业家数量和富裕程度远远不及革命前的水平。私人资本在工业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在1926年和1927年,只有4%的工业投资来自私人部门,农业的情况正好相反。 [7]
农民再次分化的信号以及农民对集体化无处不在的抵制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从1928年开始,政府重新采取强制手段获得粮食并用它来支持工业化,从而有效地把资源从私人化的农村转移到社会化的工业部门。尽管政府大力推动并且用更优惠的信贷条件提供有形的支持,仍然只有3.5%的耕地属于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占有的比例是1.5%,95%的耕地仍然为私人所有。斯大林把富农当成一种阻碍,无视集体农场的低效,选择通过武力来改变这种局面。 [8]
1930年1月,政府通过关于“在全面集体化的地区消灭富农家庭的措施”的决议,决定采取处决、流放或者收监等手段,一定要让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富裕的农民被课以几倍的重税,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较穷的农民则更容易被引诱加入集体合作社。政府加强了反富农的宣传,并且鼓励农民去抢夺土地。为了确定更多的目标,富农的范围被扩大到包含雇用劳动力,拥有生产设施(比如磨坊),以及参与商品交易的那部分人。逮捕和强制性的掠夺行为非常普通。然而,这些曾经富裕的农民早已因为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变得贫困,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中等收入,基于过时的税收记录以及为了实现政府消灭富农的目标,这些人最终没有逃过财产被剥夺的结局。矫正最终扩张到更大的社会范围。 [9]
强制手段最终取得了胜利:到1937年,93%的苏维埃农业被迫集体化,私人农场被摧毁,私人农户只能拥有小型花园大小的地块。这种转变的代价是巨大的:损失了超过一半的牲畜,大约为总资产的1/7。人们付出的生命代价更为惊人。暴力行为爆炸性地扩散。在1930年2月的几天中,有60000名“一类”富农被逮捕,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700000,在第二年的年底又上升到1800000。据估计,有大约300000名被流放的人由于恶劣的交通和流放地条件而死,也许还有600万农民被饿死。富农家庭的户主被集体流放,被认为特别危险的一些人被立即处决。 [10]
和集体化和去富农化等农村暴力性的平等化行动同步进行的,是对城市的“资产阶级专家”、“贵族”、企业家、店主和手工艺人的迫害。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这些活动一直都在持续,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150多万名市民,其中接近一半的人被处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为目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成为牺牲品。有不下7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这种制度有利于继续矫正不平等,因为它不要求给在边远地区承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人支付高工资。虽然节约的成效会被强制成本和低效率抵消一部分,但是也不能被轻视:在后来的年份中,向不受欢迎地区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显著提升了苏维埃整体的不平等水平。集体化创造了大约25万个集体农场。然而不仅农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城市居民也一样。非农场的实际工资在1928—1940年间几乎下降了一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也都出现了下降。 [11]
这些政策造成的人类苦难众所周知以至无须再详细讲述。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快速矫正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有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不仅是精英阶层,还有更为广大的中产阶级都经历了财产的被剥夺和再分配。然而,一旦经济开始改善,即便是处在始于1933年的严厉镇压的环境,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立刻出现爬升。随着人均产出和消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强劲增长,工人薪酬的差距也在扩大:“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政策要求为更高的生产率提供更高的报酬,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生活标准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即便是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这种差距永远消失。 [12]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质量不平均,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数据,我们很难准确衡量收入差距的演变。沙皇时代末期的收入集中度相当高,然而如果以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也不是特别高。大约在1904年或者1905年,其收入最高的“1%”在总收入的占比为13.5%~15%,同期的法国和德国以及10年后的美国为18%~19%。充足的土地有利于支撑农村劳动的价值。这一时期俄罗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62。我们不知道在1917—1941年间,这一数值下降了多少。根据苏联时期的数据来源,1928年工业部门工资收入的P90/P10 [02] 之比有一个较低的值——3.5。总体而言,苏联时期的基尼系数比沙皇时期要低很多。据估算在1967年,苏联非农家庭的市场基尼系数为0.229,对应整个国家在1968—1991年间为0.27~0.28。20世纪50—80年代,P90/P10的值也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的P90/P10大约为3,1984年美国的P90/P10为5.5。 [13]
“二战”后的几十年,其国家发展完全受政治干预驱动,矫正一直都在持续。在此之前极其低的农民收入,被允许比城市人口收入上升更快,而后者的收入,通过提高低工资水平、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加以平衡。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策,更有利于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溢出幅度从1945年的98%下降到1985年的6%,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出现类似下降。白领的工资下降到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即便在经济处在实质性增长的时期,专制政权都能够极为有效地平均和重组收入分配。 [14]
苏联体系终结后迎来了快速而急剧的逆转。在1988年,超过96%的劳动力被国家雇用。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4,自主就业所得还不到总收入的1/10——并且不存在财产性收入。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所说,这种分配格局重点在于由国家支付收入,集体消费,工资被压低,以及财富积累最小化。然而一旦意识形态前提不再被强制坚持,这一切就会瞬间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俄罗斯联邦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都维持在0.26~0.27之间,然而苏联垮台后,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收入基尼系数近乎翻番,1990年为0.28,5年后上升到0.51,从那以后,一直处于0.44~0.52的范围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乌克兰的基尼系数和俄罗斯差不多,然而1993年时从1992年的0.25一下子跳升到0.45,尽管后来又逐渐下降到0.3。在1989—1995年间,前社会主义全部国家的整体平均基尼系数上升了9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基尼系数表现为同步上升:除了极少的几个特例,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向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集中而其他群体收入下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俄罗斯顶层10%群体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占比从34%上升到54%。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在1980—2013年收入不平等显著上升的时期,美国顶层10%群体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44%上升到51%,在一个5~6倍长的时间内涨幅仅为前者的1/3。私人财富也出现了恢复。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0%群体控制了整个国家80%的财富。到2014年,这个国家的111个亿万富豪掌握了整个国家财富的1/5。 [15]
1991年年末,随着苏联的共产党以及苏联本身的瓦解,贫困爆发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只用了3年时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上升了3倍,达到俄罗斯总人口的1/3。当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这个比例又上升到60%。然而从长远来看,不平等程度上升也受到了工资收入放开的推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地区差异的扩大。莫斯科以及一些石油和天然气丰富地区的收入上涨异常,租金则被那些收入最高的阶层攫取。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也使财富更有可能向最富有阶层集中。 [16]
俄罗斯收入和财富从平均到再集中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化暴力的一个函数。在革命的前夕,不平等程度相当大,在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后的20年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大规模的政府强制以及鼓励穷人掠夺和他们相比不那么穷的人,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和流放。其中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没有暴力,就没有矫正。在转型过程中,只要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能维持住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不平等就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然而一旦政治压迫被取消,政治压迫由价格决定的市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混合物来替代,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就会拉大,曾位于前苏联中心地带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情况最为惊人。
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通过革命运动建立的其他共产党政权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矫正。这里我们补充几个案例。越南的土地不平等情况曾经非常严重:在1945年,3%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25%。在1945—1953年间,共产党的早期政策基本上是:优先采取通过交易进行转让、减租、对地主收取惩罚性的累进税的方式,而不是没收和征用。税收对土地所有权具有特殊的抑制作用,名义有效税率为30%~50%,一旦增加附加费,则有可能达到100%。这导致很多地主把土地出售,或者直接出让给租户。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从3%的地主占有25%的土地急剧下降为2%的地主占有10%~17%的土地。然而,从1953年开始,越共领导人变得更加强硬。其每天的工作变成对农民的动员,每个村都组织批斗会。每一个地区的政治局按照配额确定需要被惩罚的“残暴地主”名单。土改法要求没收或者强制出售最“残暴”的那部分富人的财产并对其他人进行象征性补偿。按规定“富农”不应该受到伤害,然而在一些缺少地主的地区,他们仍然会成为目标,如果他们“用封建手段来剥削土地”(即通过租赁的方式),就会被强制出卖土地。
1954年,法国人惨败后,大约80万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其中富人占多数。有大量的土地空出来并且被转交给穷人。1953—1956年间,政府发起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有很多“地主”(大约占总人口比重的5%)只剩下不足平均水平的土地,成为村子里的贱民,几千人被处决。依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土地被重新分配,因而高度平等的分配结果得以实现(除了获得更少土地的“地主”)。穷人从这种安排中获益最大。和苏联一样,平等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化行动,其结果是逐渐增多的大型集体合作社占有全部耕地的90%。1975年之后,这些政策延伸到南方。“地主”和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私人企业被国有化,并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17]
从一开始,朝鲜政权就更强势,政府最早是在1946年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集体化,直至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大型单位组织起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土地征收活动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征收的是美国人的土地,其次是面积超过67公顷的大地主的土地。到1964年,全部农地的3/4都被征收,并且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然后很快又变成国有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被国有化。1979年的尼加拉瓜,在没收了占有这个国家1/5土地的索摩查家族的土地后,获胜的桑地诺组织发动了土地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其范围又扩大到没收其他大地主的土地。结果是,在1986年,有大约一半的农业用地和一半的农村人口都卷入改革,被主要用于建立合作社或小型农场。即便如此,当桑地诺政府在1990年被选民赶下台时,尼加拉瓜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非常高,大约是0.5~0.55,和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接近,高于萨尔瓦多当时的水平,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在这种环境下,革命政府放弃暴力性强制手段,恪守民主多样性的承诺,似乎是导致矫正成效不足的决定性原因。 [18]
以列宁、斯大林所设定的激进标准来看,中美洲甚至越南所采取的再分配手段可谓相当温和,然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缺少传统标准的数据作为参考,但是毫无疑问,政府的暴力干预造成了柬埔寨全国性的大矫正。在1975年共产党获胜后的一周内,城市人口被仓促撤离,导致全国人口下降了一半,其中包括首都金边的全部人口。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国家不平等水平的重要因素,收入不平等水平因此显著下降。城市居民被划定为“新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并且多次被驱逐。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从而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他们一步步失去了财产,最初是因为撤离,然后被农民和干部蓄意剥夺,在定居农村后,更是被政府阻止享用自己辛勤种植的庄稼。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很有可能接近200万人,大约是柬埔寨全部人口的1/4。损失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大约40%的金边居民在4年后死亡。前政府的官员和高级军人被挑出来,遭受残酷的虐待。同时,由于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范围不断扩大,新精英的数量也出现下降。例如,仅仅死于臭名昭著的金边S21监狱的柬埔寨共产党员就有1.6万人之多,柬埔寨共产党员的数量在1975年的时候还不到1.4万人。在普通群众里面,导致过多人员死亡的原因可以相当平均地归结为集体化、处决、监禁,以及饥饿和疾病。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大部分的人因为头部受到铁棍、斧头以及农用工具的打击而死。部分死者的尸体被当成了肥料。 [19]
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快速自我毁灭的暴力的柬埔寨经验,不过是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极端范例。从1917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在大约60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征用、再分配、集体化以及价格控制等多种手段,共产党的革命政权成功地压低了不平等水平。在运用这些手段时,不同国家制造的暴力行为存在着巨大的数量差异,俄罗斯和柬埔寨是一端,古巴、尼加拉瓜是另外一端。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强制性矫正过程中,暴力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尽管从根本上讲,列宁、斯大林能够以较小的生命代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横扫式的征用还是严重依赖部分暴力手段以及将暴力升级的威胁。
基本的原理一直都是相同的:政府通过抑制私人财产和市场力量对社会进行重组,同时实现缩小阶级差异的目标。这些具有政治性本质的干预,代表了暴力冲击,和前面章节讨论的现代社会产生的世界大战的作用相似。在矫正不平等方面,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革命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极度依赖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无论是处于潜伏状态还是已经显露出来的)得到我们所看到的结果。这个过程耗费的巨大人力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或者间接夺走了近1亿人的生命,然而革命同样造成了数量相当的死亡。就残酷程度而言,转型性的革命和大规模动员战争是等同的——这就是我们的末日矫正四骑士中的第二位。 [20]
[01] 本书作者认为,并不是所有共产主义革命都是暴力的,也不是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产生矫正效果,强调战争对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用。作者谈及“共产主义”革命时,一些说法与我国通行的说法有不尽相同之处,此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我社同意作者说法。——编者注
[1] For Germany, France, the UK,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 herein, chapter 5, p.133.Most of the indices for Italy in Brandolini and Vecchi 2011: 39 fig.8 show moderately declining inequality between 1911 and 1921, but the resolution is insufficient to disentangle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war and its immediate aftermath, which might have witnessed a recovery.
[2] Gatrell 2005: 132–153.
[3] Leonard 2011: 63.Quote: Tuma 1965: 92–93.
[4] Tuma 1965: 92–93 (first decree); Davies 1998: 21 (further decrees); Figes 1997: 523 (“former people”).Deurbanization: Davies 1998: 22; for Petersburg, see Figes 1997: 603; see 603–612 on hunger and depopulation in urban centers for want of food.Figes 1997: 522 (Pravda);Lenin, “How to organize competition,” December 1917, quoted in Figes 1997: 524.
[5] Powelson 1988: 119 (land); Tuma 1965: 91, 94 (quotes).
[6] Tuma 1965: 96 (consequences); Powelson 1988: 120 (collectives); Leonard 2011: 67 (households);Davies 1998: 19 (inflation).
[7] NEP: Leonard 2011: 65; Tuma 1965: 96.Recovery: Leonard 2011: 66; Tuma 1965: 97.Differentiation: Tuma 1965: 97; Leonard 2011: 67.Capital: Davies 1998: 25–26.
[8] Davies 1998: 34 (grain); Tuma 1965: 99 (land); Powelson 1988: 123 (Stalin).Allen 2003: 87 notes the potential for rising rural inequality in the 1920s in the absence of communal organization.
[9] Tuma 1965: 99; Powelson 1988: 123; Werth 1999: 147–148.
[10] Leonard 2011: 69 (collectivization); Werth 1999: 146, 150–151, 155; Davies 1998: 51(violence).
[11] Werth 1999: 169, 190, 206–207, 191–192, 207; Davies 1998: 46, 48–50.Plant food consumption by peasants held steady while animal food consumption fell: Allen 2003: 81 table 4.7.
[12] Davies 1998: 54.
[02] P90/P10指顶层10%群体与底层10%群体的财富比值。——编者注
[13] Income share and Gini: Nafziger and Lindert 2013: 38, 26, 39; cf.Gregory 1982.Nafziger and Lindert 2013: 34 (ratio).Ginis: Nafziger and Lindert 2013: 34; SWIID.Ratios: Nafziger and Lindert 2013: 34.Flakierski 1992: 173 documents variation from 2.83 to 3.69 between 1964 and 1981.For a slight increase in this ratio in the 1980s, see Flakierski 1992: 183.United States: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46189.
[14] Davies 1998: 70; Flakierski 1992: 178.Of course, party elites’ access to luxury imports raised effectiv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15] Milanovic 1997: 12–13, 21–22, 40–41, 43–45; Credit Suisse 2014: 53.
[16] Treisman 2012.
[17] Inequality: Moise 1983: 150–151; cf.Nguyen 1987: 113–114 for the 1930s.Reform and outcomes: Moise 1983: 159–160, 162–165, 167, 178–179, 191–214, 222; Nguyen 1987: 274,288, 345–347, 385–451, 469–470.
[18] North Korea: Lipton 2009: 193.Rigoulot 1999 summarizes the nature of communist terror in that country.Cuba: Barraclough 1999: 18–19.Nicaragua: Kaimowitz 1989: 385–387;Barraclough 1999: 31–32.
[19] Margolin 1999a.
[20] Courtois 1999: 4 (body count).
类似的情况在以前发生过吗?在更早的时期,出现过显著矫正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革命吗?我们将再次体会到,20世纪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前现代社会并不缺少从城市和乡村爆发的民众起义,然而它们通常不能改变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大规模动员战争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在前工业化时期,革命很少成为矫正不平等的手段。
在对传统权威的早期挑战中,在大众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的法国大革命,似乎特别有希望通过冲突实现平等的目标。在旧体制临近终结的时候,法国仍然是一个收入和财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我们做出的最好的估计是,法国当时的收入基尼系数大约是0.59,和同时代的英格兰差不多,尽管估计的误差范围较大(在0.55~0.66之间)。严重不平等的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贵族占有全部土地的1/4,却免于缴纳主要的直接税,并成功抵制了一些新税,比如1695年的人头税和1749年的所得税。神职人员的情况大体相似,拥有全国1/10的土地,还得到一些钱,虽然不到财富总额的1/10,但数量仍然可观。因此,直接税几乎完全由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负担。另外,富裕的资本家可以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和官职来逃避缴税,实际的税大部分都落到农民和工人的头上。在各种间接税中,盐税是最重的一种,它强制性地对每个购买食盐的家庭征收,再一次严重打击了穷人。总体上讲,这是一种具有高度累退性质的财政税收体系。
而且,农民还承担了对贵族和教会的各种封建义务,比如徭役,以及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其他义务。只有少数农民得到了足够的土地(只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得到土地),大部分的农业人口都是佃农和无地的劳动力。在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情况进一步恶化。人口压力加大,封建权利越来越被强化,公地牧场面积缩减,导致拥有少量牲畜并且只能艰难维持生活的贫困农户被驱逐。这一切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化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1730—1780年间,土地租金翻了一番,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从事农业的人的工资上涨速度,城市工人也受到不利影响。 [1]
旧政权及其机构的解体在1789—1795年间分阶段展开,当局推行了若干有利于穷人的措施。1789年8月,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废除“个人”的封建权利,虽然拖延到了第二年才得到正式执行。尽管地租仍然有效,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行抵制,暴乱于1789年末、1790年初开始蔓延。农民闯入领主的庄园,焚烧账本。伴随着动乱,出现了广泛的暴力抗税(间接税)行为,导致征税工作停滞。1790年6月,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封建义务(例如徭役)最终被废除,公地按命令被分配给本地居民。随后的巴黎议会多次对农村的动乱做出了响应,废除了严苛的最不得人心的教会什一税。然而,由于新增加了税种,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引发了新的愤怒。“实际的”封建权利(比如每年的义务)名义上仍然有效,除非农民用年率的20~25倍的价格来买断土地对地主做出补偿,这种妥协性的安排遭到农民的抵制,他们拒绝赎买或者干脆起来造反。在1792年,农村暴力的大爆发引发了全国大范围的反封建运动,并演变成著名的“城堡里的战争”。
1792年8月,在巴黎人攻入杜伊勒里宫后,立法议会意识到需要用更广泛的改革来解决农村暴力问题:所有的土地使用者因此成为所有者,除非地主能够提供真实的地契,然而在习惯法主导的年代,地契并不常见。即便这个最后的规定也在1793年7月被雅各宾派政府废弃。至少在字面上,对一直在支付固定租金、在法律意义上是佃农实际上是小农户的几百万农民来说,这体现了对财富进行的重新分配。据估算,全国有40%的土地——那些已经被农民占有但是还没有被合法化的土地在1792年被正式私有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废除了和土地相联系的所有封建义务。需要着重注意的是,从1789年8月的反封建措施出台开始,农村改革就受到国民制宪议会对“来自下面的威胁”(群众行动)的担忧驱动。越来越趋于暴力的农民激进主义,和大都市的立法改革,被带入“一个不是导向妥协,而是导向相互激化的辩证过程”。 [2]
对土地的征收和再分配有力地推动了对不平等的矫正。1789年11月,国民议会把教会的全部土地收为国有,用来解决预算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不需要增加新税。这些土地名为国家财产,以大地块的方式进行销售,实际上更有利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场主。即便如此,据估计农民还是只获得了其中大约30%的土地。从1792年8月开始,流亡贵族的土地也被征收和出售,这次土地被划分为更小的地块,也因此更有利于穷人,这一举措反映了立法议会追求更平等的分配的愿望。农民最终获得大约40%的土地,并且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款项分摊到12年以上来购买被没收的土地。这么做能够帮助到那些条件不足的人,然而当快速的通货膨胀严重地侵蚀到贷款的利息时,这种方式对所有的买主都开始变得有吸引力。总的来说,再分配的规模十分有限:全国仅有3%的土地被农民以这种方式得到,而且贵族和逃亡者可以通过中间人来秘密收购土地。尽管没收土地对不平等有矫正效果,但也不应该被高估。 [3]
从1790年开始,国民议会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被点燃。最初有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作为支持,然而由于发行规模太大,因此5年后其损失的价值超过了原有价值的99%。这对不平等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等同于对所有人征税,其效果是累退性质的,因为富人用现金保存财富的比例比其他人要低得多。同时,通货膨胀也会在几个方面有利于穷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土地和牲畜的实际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被降低了。固定的货币型地租(逐渐替代了实物地租的交租方式)也会更加有利于租户。通货膨胀消灭了农村的债务,同样有利于穷人。另一方面,除非债务完全无效,债务人用贬值了的纸币还债,旧体制的债权人只得到部分的支付。那些购买官职然后又失去了官职的人,得到的补偿是贬值了的货币,这对精英阶层极为不利。顶级官职一般被贵族所购,这意味着投入腐败交易中的大多数资本都损失了。 [4]
旧的财富精英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仅封建特权遭到废除,教会财产也被国有化,然后流亡者及其政治对手的财产也被没收。为1793年的战争做大规模动员导致赋税增加: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地区,为了筹集所需的资金,富人被强制借出钱款。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开出了适合付款者的名单,并且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支付。另外,政府推出新税对富人进行盘剥,这些做法尽管不合法,但十分有效。在“恐怖”时期,数以千计的人以怀疑囤积或者违反价格管制的名义被收监。仅仅巴黎的革命法庭就以这些罪名宣判了181例死刑。犯人的财产被收为国有,更加刺激了人们把富人挑出来当作目标。本节标题部分的引言出自代表约瑟夫·勒庞的一次演讲,他说:“对于那些对共和国犯下罪行的人,我们应誓死砍掉那些有罪的富人的头颅。” [5]
逃离法国的贵族越来越多。最后,大约有16000人,超过贵族总人口的1/10,动身去更安全的国家。全面的迫害始于1792年。在第二年,政府下令公开销毁证明贵族身份及其封建权利的文书。然而只有很少的贵族丢掉性命:16594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当中,只有1158个是贵族,不到贵族总人数的1%。然而,贵族在死刑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并且在“大恐怖”时期达到了高潮。仅仅在1794年6月和7月的6周内,就有1300具无头尸被埋在巴黎东门外一个叫皮克普斯花园(前修道院花园)的两个坑穴里,其中1/3是贵族,包括王子、公主、公爵以及大臣、将军和高级官员,还有很多为贵族服务的平民。 [6]
留在法国并且活下来的一些人,讲述了他们的幸运和遭遇的损失。如迪富尔·德·舍韦尼伯爵所记录的:
在大革命的头三年,我损失了作为领主的23000利弗尔的收入……包括路易十五授予的由皇家财政提供的养老金以及其他几项收入……我遭遇过国民卫队的入侵、雅各宾政府的重税、各种打着爱国捐献名义的征用和没收,只保住了我的银器……我入狱4个月,造成了额外的支出……我最好的树被海军运走,不到一周之后,我又不得不把被征用的谷物运到布鲁瓦的部队仓库……还有些我没提到……我全部的领主文书都被烧毁…… [7]
只要革命让富人受损并且使穷人受益,对不平等的矫正就能够发生。即便矫正的方向明确,其程度却难以估计。在收入分配方面,废除封建义务为工人带来积极影响,对地主则产生消极影响。战争中的群众动员同样有助于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从程度上看,1789—1795年间成年男子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升1/3。在法国西部的某个地区,收获工人的工资收入占农作物收成的比重从1/6上升到1/5。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同样表现出上涨的势头:在18世纪80年代—19世纪第一个10年,工资比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更快。 [8]
在财富分配方面,土地所有权分配的变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的下降。在某个新区,1788年神职人员和贵族曾占有全部土地的42%,到180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2%,而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从30%上升到42%,然而这同样表明,中间阶层才是受益最大的群体。在法国西南部有一个地区样本:不依靠去外面打工或者救济,仅靠手中的土地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的比重从46%下降到38%,而那些有足够土地的农民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2%。从长期来看,这种转移巩固了小型农场和小块农田,确保它们在贫困条件下还能够维持下去。改革远远称不上一次彻底的对土地财富的再分配。在很多地区,拿破仑时期的最大地主属于大革命之前相同的家族,1/5~1/4被没收的土地,最后还是被原来家族的成员赎回。贵族仅仅是永久性地失去了他们1/10的土地。 [9]
克里斯蒂安·莫里森和韦恩·斯奈德有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对法国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顶层的份额出现下降,底层的份额则上升(见表8.1)。 [10]
这种比较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考察对象仅限于法国劳动阶级,精英食利阶级则被排除在外。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估计并不能让我们对大革命时期(1789—1799年)和较晚的拿破仑帝制时期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区分。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和这些数字反映的状况相比,在改革活动最激烈的18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实际发生的变化是否更大,以及大到什么程度。例如,拿破仑的追随者买下了本应该由穷人获得的土地,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有25000个家庭,其中多半是贵族,因为财产曾经被征用而得到补偿。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情况是,收入分配在18世纪90年代曾经暂时性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在一代人之后,又出现了逆转。 [11]
表8.1 法国的收入分配份额,1780—1866年

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任何结果可以和20世纪大革命造成的矫正相媲美。土地所有权、财富集中还有收入分配的改变,都发生在边缘地带。对受影响的人而言,这种影响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收入最低的40%的阶层,收入占比上涨了70%,这表明法国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境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型。产生这种结果是由于针对有产阶级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暴力行动:无论它让当代保守的观察家感到多么震惊,这种和后来的标准相比手段和雄心相对克制的革命,其带来的矫正作用还是更小。
在这个研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一次特殊的革命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原因有二:它的社群主义理想,以及造成的巨大暴力规模。1850—1864年,太平起义军控制了中国东部和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这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冲突,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运动,为千百年来大众对于“天国”的期望所激发。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这场革命,他把中国传统的群众反抗和基督教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愿景和计划。它激起了民众广泛的仇恨,从对清朝统治的抵抗、对政府官员的憎恨,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始于1851年,发轫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起义军主要由农民组成,再加上一些烧炭工和矿工。其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1852年,变成了一个500000人规模的武装队伍,1852年可能达到了200万人的规模。这个被称作“庞大的穷人军队”的队伍,席卷了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并且很快占领了南京,南京被确定为的天国的新首都。为了实现对千百万人的控制,太平军的领导人大力提倡上帝崇拜,以及一个更为世俗的目标——把汉族从外族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社会性的任务:既然只有上帝才可以拥有一切,因此,至少在概念上,私人产权的观念就不可以被接受。起义军歌颂普世的兄弟情感,这意味着所有人同属一个大家庭。这些崇高的情感在1854年年初发布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里第一次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达。它基于的前提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家人,人们放弃自己的全部私用物品,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并作为公用,平等划分每个地方的土地,让每个人衣食无忧。这是上帝派遣太平军拯救世界的原因。 [12]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等额划分,分配给成年男女,小孩能获得一半的份额,并且采用“有田同耕”的方式。按照生产力高低,土地被划分等级并进行平均分配以实现完全平等。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土地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相同的份额,就会有一些人迁移到其他能获得土地的地方。每个家庭可饲养5只鸡和2头母猪。每25个家庭可建立一个中心仓库,用于收集和储存超出他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粮食。这种高度平均主义的世俗天堂,早就存在于早期的“均田制”的观念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周期性的再分配运动从来没有实现过长久的平等。
这种监管(如果确实如此)几乎不起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方案真正得到了实施,或者广为人知。在太平军发展的早期,尽管有一些富人的房子和地产遭到了侵占,本地的村民也因此分到一部分财产,然而大部分财产还是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些活动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更广泛的再分配方案,更不用说实现系统的土地改革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农业共产主义社会。面对清政府的抵抗和最终的反攻,太平军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维持自身运转的收入。因此结果是,传统的地主–租户关系大体上保持不变。或者,最多在边缘地带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江南地区,大量清王朝时期的土地和税收档案被销毁,有很多地主,或者是逃了,或者不再能收取地租。新政权的实验,是让农民把税直接上缴给政府的代理人,然而这种做法被证明无法长久。税收可能比以前降低了,然而佃户对高地租要求的抵制也变得更加容易。太平军剥夺了富人手中清王朝时代的特权,无论用总额还是用净值计算,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分散。由于租户的强硬抵制,地主不得不承担特种税的全部份额,收入下降的压力显而易见。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导致任何系统性的矫正,“乌托邦”般的方案中的那些设想从来没有被付诸实践——甚至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之所以说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也许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普遍保留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之后,太平军的领导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封官赐爵,过上了后宫成群和宫殿遍地的奢侈生活。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太平军的暴力镇压,造成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清政府并没有镇压一个平等主义的实验,因为这样一个实验从未存在。无论是它社群主义的教义,还是它广泛的农民军事动员,都没有造成重大的矫正效果,即便它有过类似的尝试,也无法保持下去。在1917年之前,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目标和前工业化时代的客观现实之间的鸿沟,即使通过武力也无法消除。 [13]
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大体上是相同的。农民是大部分历史记载的主角,在前现代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主要由土地所有权和农产品控制权的配置决定。因此,对用革命手段矫正不平等的任何研究都应该特别关注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影响。这些事件通常很普遍: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差异,更可能与证据的性质而非实际条件有关。因此,尽管它们频繁发生,却很少有农民运动转变成能带来显著矫正效果的真正革命性的运动。 [14]
最有希望的案例,再一次地出现在比较近的时期。墨西哥1910年革命后紧随着的土地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墨西哥一直以来都经受着巨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这可以追溯到阿兹特克时期。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面积巨大的土地和数量众多的强制劳动力。1810—1821年的独立战争,克里奥尔和梅斯蒂索精英接替了富裕的半岛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富人和政府勾结,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而且还能通过日益增长的商业化获利。在革命爆发的前夕,贫富差距达到相当极端的水平。1000个家族和公司控制了总共6000个庄园,占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1600万的全国人口,2/3在农业部门就业。大部分的农民少地甚至无地。其中一半农民是对土地只拥有弱小控制权的小农,另一半则是被大农场雇用,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地租和劳役负担。债务把雇农和土地绑在一起。在墨西哥的中央州,只有0.5%的户主拥有财产,仅有856名个人拥有土地,其中的64个大农场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私人土地的一半。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的统治阶级手中。 [15]
革命始于精英派系之间的争斗,他们原本并没有土地改革的计划,但是农民因此受到鼓舞,进而追求他们自己的土地再分配目标。农民武装接管了大农场。最出名的是,在南部,由埃米利奥·萨帕塔领导的农民部队占领了大型庄园并推动了土地的再分配。激烈的农民运动造成的状况,使得影响力本已下降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着手处理。在承认公众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前提下,1917年出台的新宪法将征用合法化。这些仅仅是出于平定农民武装的需要:因此,地方暴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立法,才是驱动再分配的关键动力。即便如此,直到1920年年底,给穷人分配土地的进展依然十分缓慢,同时地主还获得了一些优惠,比如对征收进行封顶。1915—1933年,大部分再分配的土地都是品质低下的土地。直到1933年,每年只有不足1%的土地被再分配,其中,实际的耕地还不到1/4。地主可以申请禁止令,而且因为担心外国干预,对大型庄园的征收也难以推进。
“经济大萧条”造成失业增多、收入下降,最终加大了压力,土地再分配的速度在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激进派政府手中得以提升,石油工业也在1938年被国有化。1934—1940年间,大约40%的耕地被征用,雇农同样获得了分配土地的资格。土地被转交给了佃农、工人以及少地的农民,以合作农场的方式进行组织,但还是分块耕种。对基层农民的动员再次为推行这些措施提供了必要的激励。结果到1940年,有一半的土地为土地改革所覆盖,并且有一半的农村穷人因此受益。10年后,拥有土地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1910年的时候仅有3%,并且到1968年,有2/3土地被转移。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体现了在选举民主制下,大规模的再分配和矫正所面对的阻碍以及各种冲击(比如农村暴力以及后来的大萧条)在启动和加快再分配活动中的重要性。尽管墨西哥并没有出现类似于革命或激烈重组的情况,然而在面临既得利益者抵抗的情况下,对农民的动员创造出了持续推进再分配的动力。即便是更为活跃的卡德纳斯政府,也一样严重依赖这种动力输入。 [16]
20世纪50年代的玻利维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1951年和1952年的革命针对的是压迫本地农民和西语族群的寡头势力。大部分印第安人要么成为在大庄园干活的农奴,要么居住的村落被庄园夺走了最好的耕地。在起义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占领了大庄园、烧毁庄园里的房屋,迫使在外庄园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1953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改革者采取征用管理不善的大型庄园,以及缩减一部分庄园规模的措施。实际上,这次改革不过是对一直都在推进的过程的一次认可。覆盖全国农地一半以上的大型庄园被佃农以及附近的农民接收,有一半以上的穷人得到了更多的获得土地的机会。然而暴力抵抗并不总是能获得成功。1932年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萨尔瓦多农民起义短短几天内就失败了,并且还激起了军队屠杀大批农民的事件,史称“大屠杀”事件。随后推行的改革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实际上,成功的农民革命,即便在最近的历史中也不常见。我将在第12章讨论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在促进土地改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大多数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 [17]
我们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最近的历史回到前现代时期,有关中国农民运动的史料异常丰富。肯特·刚·邓研究了不少于269个的案例,他认为,这些案例是从秦初至清末的2106年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运动。“平等”,特别是和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平等,作为目标被一再提出来,在反叛组织推行的措施中,财富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多数的运动并不成功,但仍然对鼓励税收改革和推动土地再分配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在这些案例中,反叛者力图推翻现有的政权,扮演“腐败政府机关的终结者”和财富再分配者的角色。在下一章,我们将在国家崩溃及其矫正效果的背景下回到这个问题。 [18]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叛者明确提出了平等的目标,然而即使是反叛成功,产生实质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完全没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据说是放羊倌的反叛领袖,指挥着主要成员是农民的大型军队,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1644年,在被扩张的满人摧毁之前,他短暂地在北京自封为皇帝。虽然据说他蔑视财富,计划将富人的财产没收并进行再分配,甚至还要平均地权,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和两个世纪后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情况相同。 [19]
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因其独有的时间深度显得尤为突出。其他的古代社会能够提供的史料则要少很多。也许这并不是偶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发生的是奴隶起义或者是与之相似的事件,并不是农民运动。从原则上讲,奴隶大规模地获得自由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矫正机制:在奴隶数量充足的环境,奴隶代表的是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大量的资本,如果突然失去这种资本,将使财富分配的总体水平趋于平等。本书第6章描述的美国旧南方出现的平等化紧随在美国内战之后,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据说在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的入侵导致超过2万雅典奴隶逃跑,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这仅是一次面对国内战争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反应,并不是狭义上的造反。公元前370年,当美塞尼亚农奴——由斯巴达勇士–市民阶层拥有的公共奴隶因外来干涉而获得了自由时,相似的矫正也一定发生过。然而,这又是一次非自发的农奴运动。实际上,稍早前,在公元前462年发生的一次农奴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奴隶运动(大约在公元前136—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1年)如果能建立起独立的奴隶“王国”,就有可能通过剥夺大地主的房产和收入的手段实现矫正的目标。然而它们都没能获得成功,发生在公元前73—前71年的意大利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叛乱也没能获得成功。
后来罗马帝国的某些团体采取的暴力行为,经常表现出与农村动乱或造反所具有的平等愿望相似的特征。然而,把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罗马北非地区的围剿者看成某种“扎克雷”式农民起义的当代共识则缺乏实证基础,不过是用敌对的修辞把他们描述成对社会的威胁——“农村造反是反抗地主”与“信用票据来自债权人的勒索,应该归还给债务人”代表着阶级斗争保存下来的两条主要控诉。仅能确定的是,这个团体由暴力的流浪收割工人构成,他们在圣奥古斯丁时期曾经卷入基督教派别冲突。罗马高卢地区的巴高达人是一个更能让人信服的案例:他们首次以造反者出现是在公元3世纪,5世纪时又再次出现,明显是和罗马统治出现危机和弱化有关。他们宣布或者试图宣布地方控制,也许只是寻求填补权力的空缺:其中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属于农民起义或阶级冲突,虽然存在很少量的证据让它有时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20]
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有关农民起义的消息开始自由地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城市动乱,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据统计,仅仅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就发生了不少于60次的农民造反运动和大约200次城市起义,一项范围更大的对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的调查,收集到了更多的案例。1323—1328年发生的弗拉芒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并且在早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大范围的成功。农民武装最初和城市选民结盟,赶走了贵族和骑士,并流放贵族和官员。1323年,造反的布鲁日市民抓获了弗拉芒的统治者路易斯伯爵,囚禁了他5个月之久,而且叛军一直控制着佛兰德斯的大部分地区。城乡利益冲突和法国军事干预的威胁,带来了1326年的和平,农民自治受到严重限制,并被要求加罚款和支付欠款。由于群众委员会挑选的农民领导人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些条款立即招致农民造反分子的拒绝。他们继续前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政权,直至1328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在农民控制的地区,发生的矫正效果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没收了被驱逐者的土地进行再分配,靠税收和法庭建立自治。
平民对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地主进行了反抗……他们为自己的城堡选出了首领,成立了非法的武装。他们冲出去,俘虏了所有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地主和收税员。如果地主逃了,他们就摧毁地主的庄园……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平民或者乡下人……他们焚烧了贵族的豪宅……掠夺了他们在西佛兰德斯的全部财产。 [21]
后来的赔偿声明显示,对富裕地主的可移动物品和农作物的征用是有序进行的。然而不太确定的一点是,那些对反叛者的极端和暴力行为的指控是充满敌意的宣传还是基于事实:与杀害富人的暴行相关的证据零碎且可疑。相反,叛军被击败后,在卡塞尔地区对反叛者进行的野蛮报复导致3000多农民死亡的事件却被很好地记录在案。获胜的法国骑兵部队很快就开始屠杀平民,叛军首领也被逮捕和处决:
获胜后,法国的光荣君主并没有用善意来看待这些事情;国王是凭借上帝的全能实行统治的……他焚毁农民的村子,屠杀反叛分子的妻儿,为了留下永久记忆而对他们的罪行和叛乱进行报复。
随后是迅速的和解,伴随着压倒性的欠款和赔偿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造反失败源于它的成功:被严重动摇根基的精英集团,带着教皇的祝福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圣战武装,赶在其他地区的农民跟进弗拉芒的榜样之前将其镇压。因初级生产者的武装反抗而引发镇压力量,这是一个早期但有力的案例。在这种环境下,持续的矫正无法实现。 [22]
1358年发生在法国北部的“扎克雷”农民造反也是如此。然而,和弗拉芒起义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持续了两周,而且明显缺乏组织架构。农民袭击并摧毁了贵族的城堡和大宅,直到在梅洛战役中被马背上的骑士击败。精英集团记录了据说是农村暴民的恶行,其中,最恶劣的是让·德·贝尔描述的恶名昭著的行为——一个骑士当着妻儿的面被架着烤:
扛着武器和军旗,他们占领了乡村。他们到处杀人,屠杀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贵族,甚至还包括他们自己的领主,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把贵族的房屋和城堡夷为平地……让贵族当着自己的妇人和孩子的面悲惨地死去。
然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农民实际上做了什么,统治阶级做出的反应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恢复力量,带着复仇的渴望,骑士和贵族团结起来了。他们跑遍了乡村,四处放火,残忍地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农民,而不仅仅针对给他们造成伤害的那部分人。 [23]
无论实际的行为有多么暴力,这种地方性的起义并不可能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甚至连部分例外的例子都没有几个。比如,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很显然失败了。起义被为筹集对法战争经费而开征新税激发,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被人民渴望保护自身收益的想法驱动的,黑死病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劳动法规和封建制度控制收益。这次运动很快被镇压了,尽管在此之前,反叛分子曾经占领了伦敦塔,洗劫了首都的宫殿和豪宅,亲自会见国王查理二世,并处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席大法官等大人物。动乱曾席卷大半个英国,尽管大多是在东部。无论反叛者是否真的计划了很多更激进和无情的暴行:他们绝不退却,直到所有的贵族和富豪被彻底消灭。
正如亨利·奈顿带有偏见地断言,没有哪一次造反能够获得成功。这一次造反行动在几周内就结束了:造反领导人被抓并被处决,超过1000个造反分子丧生。然而,尽管瓦特·泰勒的要求——“所有的人必须获得自由!”遭到致命的武力回击,尽管劳动法规仍然被保留,农奴制也没有被废除,毫无疑问,工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持续的改善。但这与遭人嫉恨的人头税的下降关系不大。一种比反叛武装更加强大的暴力使矫正过程获得了推进的动力:卷土重来的瘟疫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在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和不平等做斗争的时候,细菌比人类的任何一次造反行动都更加有效。无论农民的暴力还是精英的反暴力,都远远不及大规模流行病造成的致死率。 [24]
只有极少的暴力能直接改善不平等状况,尽管只是暂时的。1401—1404年间,佛罗伦萨境内有超过200个山村造反,根据帕戈洛·莫雷利的记录,“没有一个农民不是欢天喜地地去佛罗伦萨并且要把它毁灭”,他们的决心足以使他们从城市的统治者那里获取其物质上的让步,尤其是免税和免除债务。然而,实质性的矫正效果并没有可能通过所谓的规定被保留下来。1462—1472年间,由于黑死病造成劳动力稀缺,封建领主压力日益增加,在加泰罗尼亚爆发的农奴叛乱同样也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其他分别于1450年、1484年以及1485年发生的西班牙叛乱也都以失败告终。在1514年,因被暴君要求参加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匈牙利的农民也造反了。在乔治·多萨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庄园、杀死地主,然而军事失利使他们面临恐怖的浪潮。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西欧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覆盖了德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试图保住瘟疫过后的收入,抵抗庄园主的封建权力以及其对公地的侵占,而且因为各种反权威思想的传播,这些目标得到了加强。虽然农民武装袭击了城堡,并且得到了修道院的支援,然而他们并不是寻求全面的矫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减税、限制或者废除庄园主的特权和农奴制。更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仍然被边缘化,例如迈克尔·盖斯迈尔呼吁要废除地位差异以及把房屋和矿产国有化。失败是普遍并且血腥的:在一系列战斗失利后,估计有为数10万的农民在战争以及随后的镇压中丧生。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精英集团的回应比农民的行为要残暴得多。 [25]
历史一直都是这样继续着。在1278年,保加利亚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农民皇帝”的短命统治之下。养猪倌伊瓦伊洛,号召农民起来反抗鞑靼人的入侵,赶走了当时的统治者。然而和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把他的反抗看成一种社会运动相反,现代学者发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和他的追随者对社会不公进行过反抗,或者是寻求过任何社会变革”——当然无论如何,他仅仅坚持了一年时间。1670年和1671年,在哥萨克人的支持下,俄罗斯南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斯捷潘·拉津发表了颠覆性的声明,其中的一条是要求惩治名流精英,废除等级和特权,促进哥萨克人的平等地位。运动在充满血腥的失败中结束。很多其他的例子也都是如此,1549年英格兰凯特起义,直接针对的是限制农民生计的圈地运动。1773—1775年的俄罗斯哥萨克叛乱,主要反抗农奴制的强化;1790年的撒克逊农民起义,是出于对贵族通过狩猎特权掠夺田地的愤怒;1846年的加利西亚农民起义针对的是封建特权;1921年的印度马拉博叛乱,同样是因地主权力被强化而发生的反抗。 [26]
现代人试图给混乱事件强加逻辑,以确定具体的民众关切和叛乱的原因。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斯,和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仍然是罕见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反叛则常见得多,并且往往是因为财政被滥用。14世纪下半叶,因黑死病失控导致造反激增;16世纪的造反是出于对复活农奴制的抵制;在17世纪,则主要是反抗政府财政的扩张,直接税对农村的打击远比对城市的打击更为严重;最后,在18世纪后期,农民造反主要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早就应该废除不合时宜的地役权了。农民造反在开始的阶段经常表现为抗税,包括1323—1328年的佛兰德斯农民叛乱,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1382年鲁昂的“哈雷尔”叛乱,1437年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造反,1514年符腾堡州的“穷人康拉德”叛乱,1515年的斯洛文尼亚农民造反,1542—1543年的瑞典达克战争,1595—1596年的芬兰俱乐部战争,1594—1707年间的4次法国农民起义,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1794—1804年的中国白莲教叛乱,1834年的巴勒斯坦农民造反,1862年的朝鲜农民造反,1906年和1907年的罗马尼亚农民叛乱的开始阶段,以及1920年和1921年的坦波夫反苏维埃战争。在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894年的朝鲜东学党起义,17世纪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主要的起义中,它也是一个基本的元素。以上列举仅仅是代表性的,并不完整。 [27]
和中世纪后期的例子相似,早期的现代农民运动很少能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产生显著的影响。德国农民战争为德国南部的农民赢得从长期看有利于他们的让步,成功抑制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扩散——这种保护将他们和没有参加起义的北部和东部的农民分隔开。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更为迅速地造成税负下降和债务减免。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例子中出现的暴力反抗可能会有所不同,总体的面貌却十分清晰:明显的矫正并不在前现代农民造反的范畴以内。这是一个包含了愿望和能力的函数。正如伊芙–玛丽·贝尔塞的观察:“很少有造反能够成功夺取全部权力;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这么做。”的确,如同14世纪20年代的弗拉芒农民运动可能做过的一样,当他们离成功越近,释放出来的负能量就会越强大。 [28]
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甚至更适用于城市起义。在大多数的历史环境中,城市都是被广大的农村包围,人口的数量也远远不及农村人口。通过调动士兵、武器和周边地区的资源,统治者和贵族很容易就能平息发生在城镇的叛乱。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只是一个近期的例子。如果说市民起义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的话,那应该是在那些自治的城市国家,因为当地的精英集团并不能随意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平息叛乱。
在第6章,古希腊被看作大规模军事动员和共生性平等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问题由此产生:是否这种环境也能产生目标在于或者已经实现全面矫正的革命运动。激进的愿景当然会出现在戏剧或者乌托邦作品里。公元前392年,雅典上演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议会中的妇女》(Ekklesiazusai ),里面的雅典妇女废除了私人财产和家庭,颁布了人人平等的法令。4年后,在他的另一部喜剧《财神》(Ploutos)里,主人的不当财富被没收。在《理想国》(Republic )这本书里,柏拉图曾经被一个想法困扰,这个想法是“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是有两个,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家”。在后来的著作《法律篇》(Laws )里,他设想最富和最穷市民的非土地财富的最大比例为4∶1。更加激进的乌托邦理想走得更远: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欧赫迈罗斯构想了一个叫潘加耶的岛,岛上的居民除了房屋和花园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大多数人都得到相同的生活用品。同一个世纪后期,伊本布洛斯描绘了一个太阳岛,岛上完全没有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人人平等、幸福美满。 [29]
然而,在古希腊的实践中,这些事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和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重大的矫正需要重大的力量。有据可查的最极端例子,可能是发生于公元前370年的阿戈斯的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一场内战:当时有1200个富裕的市民在模拟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且被人用棍子殴打致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交给大众。我们将会在第12章看到,伴随着政变的土地改革的记录虽然十分丰富,依然缺少我们在现代的革命环境中看到的那种大规模暴力。 [30]
真正激进的城市动乱一般都很少见。一个有名的例子和1342—1350年的帖撒罗尼迦城的“狂热者”有关:普通群众取得了城市的控制权,他们杀死贵族,没收了其财产并且重新进行分配。一些含有敌意的记载把他们视为极端主义分子,然而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过一个系统性的没收和再分配的方案。除了古希腊城邦文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意大利通常由独立的城邦国家群组成,是另一个可能产生雄心勃勃的城市运动的重要候选者。事实上,城市起义经常能被记录下来。然而和农民运动并不会频繁地跟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相似,城市的暴力运动,即使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很少把目标指向资本家和雇主。由腐败和行业的排挤引起的骚乱更为常见,就比如抗税起义。而且,和农民起义仍然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尽管城市起义的目标相当温和,但仍然容易失败。一个很好的案例是著名的1378年佛罗伦萨的琼皮起义,其起因是纺织工人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这个行会制造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尽管曾经成功接管了城市,但他们的要求很温和:新建行会进行合并,以及对财富征税。即便如此,这场运动最后还是被血腥镇压了。 [31]
这是《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在谈及1358年短命的“扎克雷”农民起义时所说的话——已被证明是贯穿历史的共同主题。1932年发生萨尔瓦多农民起义,在后来的镇压过程中,政府军屠杀民众,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据估计屠杀人数为8000~40000人。这种结果并不是完全出乎预料:因为在起义开始之前,叛军领导人阿方索·卢纳告诉政府的作战部长华金·巴尔德斯,“农民将用他们的砍刀赢得你们拒绝给他们的权利”,然而后者的回答是,“你们有砍刀,我们有机枪”。由于没有获得伊芙·玛丽·贝尔塞所说的“全部的权力”,农民起义并不能消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即便这曾经是(虽然很少是)他们的目标。20世纪见证的巨大动乱所具有的暴力性征用和控制手段,并不适用于前现代社会。而且,它们还缺少坚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制造“恐怖”而备受非议的雅各宾派,也回避了全面的征用和平等化。他们并不知道,全国范围的真实恐怖最后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32]
所以,通过暴力起义来进行有意识的系统性矫正超出了前工业化时代革命者的手段。20世纪,我们才看到既拥有机枪又拥有激进方案的革命。只有在那个时候,《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的结论才能够适用于另一端的领主和地主——最初始的1%。只有在那个时候,武力才足以被普遍地使用、获得充分转型的结果,并且持续的时间足以等到实质性的矫正的产生。虽然在前现代社会,暴力性的民众不满行为并不罕见,然而在社会的演变中,暴力能力及其适用范围提升后,才能追求激进的平等化政策,无论其成本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而言有多高。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最终的转折点。即使社会被无情的革命者深入渗透,被强制执行的平等化也只能维持在这些政权执政期间。一旦他们失去权力,要么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或者柬埔寨一样改变路径,要么像越南一样,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迅速回升。这种规律甚至适用于极为不同的环境,事实证明:前者会出现经济崩溃和爆发性的不平等状况,后者会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和逐渐上升的不平等。 [33]
这种由“现代的”且经常是血淋淋的转型式革命带来的矫正,只有在潜在的或者公开的暴力本质能够抑制住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被维持下去。一旦压力减小或者消除,平等化就会被逆转。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6~0.27上升到2011年的0.51。越南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2010年可能达到0.45,尽管有更低的值同样被引用,柬埔寨2009年的基尼系数据估计达到0.51。古巴的发展也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1959年,古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55或者0.57,到1986年,下降到0.22,然后又似乎上涨到1999年的0.41和2004年的0.42,尽管还有一种估计——1995年高达0.55。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是经济自由化导致不平等水平快速上升。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国家。关于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共产主义是否带来了任何价值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更大的物质平等而言,无论它曾经以如此血腥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34]
[1] Inequality: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69–70 and 61–70 on prerevolutionary inequality in general.See also Komlos, Hau, and Bourguinat 2003: 177–178 for French eighteenthcentury body height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class.Tax system: Aftalion 1990: 12–15; Tuma 1965: 59–60.Access to land: Hoffman 1996: 36–37; Sutherland 2003: 44–45.Aftalion 1990:32–33 (peasants, worsening); Marzagalli 2015: 9 (rents and prices).
[2] Tuma 1965: 56–57, 60–62; Plack 2015: 347–352; Aftalion 1990: 32, 108.Quote: Plack 2015:347, from Markof f 1996a.See also Horn 2015: 609.
[3] Tuma 1965: 62–63; Aftalion 1990: 99–100, 187; Plack 2015: 354–355.
[4] Aftalion 1990: 100, 185–186;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71–72; Postel-Vinay 1989: 1042;Doyle 2009: 297.
[5] Aftalion 1990: 130–131, 159–160.
[6] Doyle 2009: 249–310, esp.287–289, 291–293.
[7] Quoted from Doyle 2009: 297–298.
[8] Leveling: see esp.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70–72 and Aftalion 1990: 185–187.Real wages: Postel-Vinay 1989: 1025–1026, 1030;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71.
[9]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71; Aftalion 1990: 193; Doyle 2009: 294.
[10] Table 8.1 from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74 table 8.But cf.ibid.71: “There are no viable 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approximate how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hanged between 1790 and the 1830s.”
[11] Morrisson and Snyder 2000: 69 table 6 put the prerevolutionary top decile income share at 47 percent to 52 percent.Post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s: Tuma 1965: 66; Doyle 2009: 295.For private wealth shares, cf.Piketty 2014: 341.
[12] Kuhn 1978: 273–279 (quote: 278); Platt 2012: 18; Bernhardt 1992: 101; Spence 1996: 173(quote).
[13] See Bernhardt 1992: 102 for the lack of evidence of its ever even being mentioned in records from Jiangnan.Relations: Kuhn 1978: 279–280; 293–294; Bernhardt 1992: 103–105, 116.
[14] The quote in the section caption is from Thomas Walsingham’s account of the English peasant revolt of 1381, quoted from Dobson 1983: 132.
[15] Tuma 1965: 111; Powelson 1988: 218–229; Barraclough 1999: 10–11.
[16] Tuma 1965: 121–123; Barraclough 1999: 12; Lipton 2009: 277.
[17] Bolivia: Tuma 1965: 118, 120–123, 127–128; Barraclough 1999: 12, 14–16; Lipton 2009: 277.El Salvador: Anderson 1971; and see also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On land reform more generally, see herein, chapter 12, pp.346–359.
[18] Deng 1999: 363–376, 247 table 4.4, 251 (quote).Although most recorded rebellions failed,no fewer than forty-eight new regimes were installed by rebels in that period (223–224 table 4.1).Most rebellions were launched by rural unrest.
[19] Mousnier 1970: 290.
[20] Circumcelliones: Shaw 2011: 630–720 (quotes from Augustine on 695–696), and 828–839 for a dissec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ical constructs.Bagaudae: e.g., Thompson 1952,rejected by Drinkwater 1992.
[21] See Fourquin 1978 on popular rebellion in the Middle Ages; Cohn 2006 on social revol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with the collection of sources in Cohn 2004; Mollat and Wolff 1973 specifically on the later fourteenth century; Neveux 1997 on the fourte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also Blickle 1988.For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see Mousnier 1970 o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and see Bercé 1987 on peasant wars in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For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see Katajala 2004.Numbers: Blickle 1988: 8, 13 (Germany).Cohn 2006 covers more than a thousand events, about a hundred of which are documented in Cohn 2004.Flanders: TeBrake 1993; see also Cohn 2004: 36–39 for sources.Chronicon comitum Flandrensium, quoted from Cohn 2004: 36–37.
[22] TeBrake 1993: 113–119, 123, 132–133; Chronicon comitum Flandrensium, quoted from Cohn 2004: 37.
[23] Cohn 2004: 143–200 on the rebellion, and 152 for the roasted knight.Quotes: Chronique of Jean de Venette, in Cohn 2004: 171–172.
[24] 1381: Hilton 1973; Hilton and Aston, eds.1984; Dunn 2004.Dobson 1983 collects sources.Quotes: Chronicon Henrici Knighton, in Dobson 1983: 136, and Tyler as paraphrased by the Anonimalle Chronicle, in Dobson 1983: 165.
[25] Florence: Cohn 2006: 49–50, with sources in Cohn 2004: 367–370.Spain: Powelson 1988:87.Germany: Blickle 1988: 30; 1983: 24–25.Gaismair: ibid., 224–225, and cf.223–236 for other radicals.Failure: 246; 1988: 31.
[26] For Bulgaria, see Fine 1987: 195–198 (quote: 196).Cossacks: Mousnier 1970: 226.
[27] Middle Ages: Cohn 2006: 27–35, 47.Black Death: esp.Mollat and Wolf f 1973, with Cohn 2006: 228–242.Later phases: Bercé 1987: 220.
[28] Bercé 1987: 157, 179, 218 (quote).
[29] Fuks 1984: 19, 21, 25–26.
[30] Argos: Fuks 1984: 30, mostly based on Diodorus 15.57–58.
[31] Thessalonica: Barker 2004: 16–21, esp.19.Italy: Cohn 2006: 53–75.The section heading is taken from Niccola della Turcia’s Cronache di Viterbo, reporting the motto of rebels in Viterbo in 1282 when local nobles were chased out of the city, quoted from Cohn 2004: 48.Causes: Cohn 2006: 74, 97.Ciompi: Cohn 2004: 201–260 for sources.
[32] Jacquerie: Anonymous, about 1397–1399, quoted from Cohn 2004: 162.El Salvador:Anderson 1971: 135–136, 92 (quotes).Quote: herein, p.250.Jacobins: Gross 1997.
[33] See Milanovic 2013: 14 fig.6.
[34] Ranis and Kosack 2004: 5; Farber 2011: 86; Henken, Celaya, and Castellanos 2013: 214; but cf.also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2: 6 for caution and Veltmeyer and Rushton 2012: 304 for a lower Cuban estimate for 2000 (0.38).SWIID registers a decline from 0.44 in 1962 to 0.35 in 1973 and 0.34 in 1978.In view of this, the question whether communism’s effect on social policy in Western nations (see herein, chapter 5, pp.172–173) has been its most durabl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equalization is worth considering.
战争和革命释放的暴力越多,对社会的渗透越深入,它们就越有可能降低不平等。但是如果这些动乱摧毁了整个国家和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呢?根据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我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强的矫正效果而期待更大的动乱。这一冷酷的预测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支持。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颠覆了等级制度,并且通常大幅度地降低了物质方面的不平等。和前面章节讨论过的主要发生在更近期的过程不同,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我们从定义专业术语开始。大型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和严重程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些过程主要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关,一般我们称之为国家衰败。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如果不能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腐败、缺乏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崩溃,以及丧失合法性是国家衰败的标志。然而这些标准并不适用于更遥远的过去。这一概念认为国家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基本的安全,国家的失败或者崩溃可以从它们无法满足这种期望中推断出来,然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出于全球性研究的目的,我们最好采用对基础性国家功能的一个大概描述。由于前现代国家的政治首先是专注于检查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保护统治者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征收执行这些任务和满足权力精英致富所需的收入,国家衰败最好被理解为丧失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能力。对主体和领地的控制遭到侵蚀以及政府官员被类似于军阀这种非政府角色取代是典型的结果,在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力甚至可能被下移至社会基层。 [1]
另一方面,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系统崩溃,这是一个远远超出了政治治理机构的失败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并且经常是包含一切的瓦解过程,系统崩溃被定义为“已建立的社会复杂性的快速且显著的丧失”。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知识领域,它通常会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化和分工的弱化,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减缓,以及对庞大的建筑、艺术、文学和文字这些文明象征的投资下降。这些变化伴随着政治瓦解并且相互作用,削弱或完全消除集中的控制功能。在严重的情况下,人口总体上会减少,居住地会萎缩或被抛弃,经济活动会倒退到较为低级的水平。 [2]
国家或者整个文明的崩溃对我们认识矫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力量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讨论内战的影响时所看到的,国家衰败可能为少数人创造新的致富机会。然而原来的精英很可能会受到损害,在较大的国家分裂成几个较小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最顶层的资源集中潜力将会下降。系统崩溃必然对权贵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央集权制的解体破坏了正式的等级制度和精英阶层,并且阻止了后者立即被希望在类似的范围内进行运作的竞争对手取代。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充分的书面证据,并且这些文字记录经常会在(系统)崩溃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从代替物上推断精英阶层的衰落,用著名的系统崩溃考古学家和理论家科林·伦弗鲁的话来说就是“停止富裕的传统墓葬……放弃豪华的住宅,或者重新采用‘贫民窟’的穷人风格……停止使用昂贵的奢侈品”。 [3]
国家衰败是一种强大的矫正手段,因为它以多种方式妨碍了统治阶级走向富裕。正如我们在开篇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财富主要有两个来源——通过投资土地、贸易和金融这类生产性的资产和经济活动进行资源积累,以及通过国家服务、贪污和掠夺进行掠夺性积累。两种收入来源都非常依赖国家的稳定,前者因为国家权力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保护,后者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国家机构是生成和分配收益的工具,国家衰败可能会降低资本回报,彻底抹去通过行使或者接近政治权力获得的利润。
其结果是,原来的精英遭遇大规模的损失。政治动荡不仅剥夺了他们继续敛财的机会,同时也威胁到他们现有的财产。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下降有可能降低不平等性:一方面,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的时候,虽然每个人的资产和生存都会面临风险,但是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穷人大得多。一个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民家庭只能承受相对有限的收入损失。更大的损失可能威胁到其成员的生存,但那些死亡或流亡的人口不再属于这一特定群体,因此不再参与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即使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或财产,富人也能生存下来。旧权贵中的那些经受住暴风雨生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留下来的但多少已被削弱领导地位的人,不管在绝对量还是在相对量上,最终与之前相比很大可能都会穷得多。
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之后,物质差异的压缩是不同程度贫困化的一个结果:即使这些事件导致大多数或所有人都比以前更糟,富人的损失都会更大。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政治解体会阻碍对剩余的攫取,平民的生活水平有时候甚至能获得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矫正不仅仅是一场以不同速度触底的比赛结果,而且还可能因为劳动人口的收益增加而得到加强。然而,由于证据的性质,记录精英阶层的衰落一般来说要比识别贫困阶层同期取得的改善更容易或者至少不会那么困难。因此,我主要关注的是权贵阶层财富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含义。我的讨论从那些具有最佳的文献记录的前现代国家案例的研究开始。在继续考察那些检验我们知识局限的不明确的证据之后,我将用索马里国家衰败的现代案例得出结论,看看在当今世界是否仍然可以观察得到其所反映的平等化特征。
中国唐朝末期异常清晰地展现了国家的解体如何导致精英财富的覆灭。唐朝始建于公元618年,由唐高祖在短命的隋朝基础上建立,隋朝曾成功地在汉朝和西晋控制的广大疆域上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在唐代,最初的土地分配方案旨在使人们平等地获取资源,然而逐渐让位于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到帝国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少数显赫家族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虽然单个家庭无法使几代人都保持顶尖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长达几个世纪。拥有高级公职的特权刺激个人发财致富,这一过程仅会受到家族争斗和最终更加暴力的帮派争斗的阻碍,然而这些也只能抑制和逆转单个家庭的崛起,并不能破坏他们对公共服务最有利可图职位的集体控制。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拥有贵族头衔的家庭以及所有的官员和官阶的拥有者,甚至皇室家族的远亲,都被免于纳税和劳役,这是一种明显的公开倾向于权势和具有良好人脉关系阶层的累退制度。这个集团的成员私下购买公共土地,虽然统治者一再禁止,但未成功阻止这类行为。
结果,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权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得到扩张,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实施土地均等化方案的尝试被终止。大地产的发展使农民免于向国家交税,允许业主将农业剩余转化为私人租金。与长途贸易相联系,这些商业化的地产有助于维持日益富裕的精英阶层。那些投入充足的资本用于运营磨坊的人,将水从农民手中转走,这一做法招致了农民的不满,但政府只是偶尔进行干预。公元8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声称:
贵族、政府官员和有实力的本地家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庄园,吞噬农民的土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所谓的法规……他们非法购买农民的均田制土地……导致农民无立足之地。
这也许是一种依赖于刻板印象的夸张说法,但不管怎么说,它触及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土地财富的持续集中。最大的差距存在于最顶层,公元6世纪与7世纪紧密附着于朝廷的那些家族,放弃他们当地的领地迁往长安和洛阳这些都城,因为那里最靠近王权,可以确保最迅速地获取政治权力和财富。这种空间集群有助于确保其获得高级的中央职位和地方官职。和很少能够上升到国家机关的地方上流阶级不同,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央精英阶层。一份最为详细的、对这个群体和它留下的大量的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在公元9世纪,住在长安的皇家知名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大臣和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最高级别官员,其中至少有3/5存在着紧密相连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因此,这个“高度封闭的婚姻和亲属关系网”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为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服务。 [4]
然而,在大都市居住也是有代价的:虽然在秩序稳定的时期有很高的回报,但是当统治者不再能够抵抗篡位者的挑战时,这些顶层的唐朝精英就会被暴露在暴力行为中。公元881年,叛军黄巢占领了首都长安。高层官员的抵抗引发了暴力的报复行动,仅仅几天之内,4名主要的现任或前任大臣被杀或自杀,数百人丧生。黄巢很快就失去对他军队的控制,在这个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惊人财富的城市里,这些人横冲直撞、大肆抢劫。有权势的名流成为最受欢迎的目标:据一个消息称,士兵“尤其憎恨官僚,杀死了他们抓到的所有的人”。据说因为一首讽刺诗的发表,有3000名文人被屠杀。而这仅仅是开始:尽管黄巢叛乱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长安多次被争斗中的群雄洗劫一空,这些事件摧毁了这座城市,并且使当地居民陷入贫困。郑谷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
可悲闻玉笛,不见走香车。
长安附近的富人财产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韦庄,最大资本家族之一的后代,如此描述了他的家族房屋周围的荒凉:
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
桑树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郑谷为他的表弟王斌的财产的命运发出了哀叹:
枯桑河上村,寥落旧田园,
……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
久歉家僮散,初晴野荠繁。 [5]
在这些经常发生的危机过程中,丢掉性命的贵族很有可能有几千人,幸存下来的人被夺去城市里的住房和郊区的地产。清洗运动一直持续到过去的权贵势力所剩无几。公元886年,在一次政变失败后,数百名支持政变的官员被处决。公元900年,在获悉一个试图消灭他们的阴谋后,朝廷的宦官杀死了几乎所有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然而在第二年,这些宦官及其盟友遭到报复又被全部消灭。在公元905年的一次事件中,仍然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7位大臣被杀,尸体被扔进了黄河。这些连环暴行快速扩散,彻底消灭了大都市权贵。
暴力迅速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公元885年,洛阳被洗劫和摧毁,从公元9世纪80年代—10世纪20年代,整个国家的各个地方中心也陷入了战争和清洗运动,给当地上层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家又一家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
在每一个地方,那些有着精心制作的屋檐的精美豪宅,被烧得精光。 [6]
最后几乎无人幸免。中央统治阶级迅速消失,到公元10世纪后期,几乎完全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在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和负担得起精致墓地的那些人有关的墓志铭在公元881年的暴力事件之后变得极为罕见。地方的权贵分支并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通常可以从一些知名的幸存者悲伤的作品中得知,他们大都失去了财产。随着祖传的财富消失,社会关系瓦解,他们无法重获权势的地位。从公元960年开始,一个新王朝宋的出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家族,他们来自地方,在中央机构重建的过程中抓住了权力的手杖。 [7]
唐朝贵族暴力且全面的毁灭可能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表现了国家衰败是如何毁灭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财富,通过使富人致贫甚至消灭富人的手段来矫正财产的分配。即使如此,不是直接针对国家精英的暴力也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矫正。国家衰败使他们失去了从政治职位和政治关系以及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因为他们曾经控制的国家失去了领土,以及被外来挑战者夺走财产也使得他们的财富减少。所有这些情况的总体结果是相似的,即使很难用任何有意义的术语来衡量:通过切断收入分配曲线尾部(在洛伦兹曲线上)的最上端以及极大地压缩顶层群体在总收入和财富中的比例以实现不平等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富人比穷人遭受的损失更多,无论国家衰败是否导致了普遍的贫困,还是主要破坏精英群体,平等化都很可能发生。 [8]
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造成财富精英的毁灭是一个不那么血腥,但并不逊色的揭示国家衰败带来矫正不平等的案例。到公元5世纪早期,巨大的物质资源最终落入一个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型统治集团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地中海盆地西部地区,由意大利最初的核心和广阔的伊比利亚半岛、高卢(现在的法国)以及北非的领土组成。根据历史悠久的传统,罗马的枢密院主要由最富裕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罗马人构成,逐渐被几个极少数强大的、位于罗马城内的关系紧密的家族主导。据说,这些超级富豪“拥有的地产几乎遍布整个罗马世界”。一个真实的例子中提及,一对夫妇在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北非、西班牙和英国都拥有财产。婚姻和继承的结果、官员们的办公财产以及跨地区的土地财富得以维持,不仅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且还得益于国家支持的、为财政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这使得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可靠的贸易网络中受益。和中国的唐朝一样,参议员拥有对附加税和服务义务的豁免权,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却沉重压榨了下层精英阶层。最后,据称最富有的家族的年收入可以与整个省份的收入相媲美,并在罗马和其他地方拥有豪华的住所。最富有的地方权贵,虽然无法与中央精英竞争,但也同样受益于与帝国的联系:据说两个来自高卢的地主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南巴尔干地区都拥有房产。 [9]
在创造顶层的有产阶级梯队的过程中,跨地区积累财富和保持赢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一个拥有数千万臣民的帝国中,特权阶层能够获得高层政治职位,国家统治中贪污和腐败是例行公事,最富有、最具权势的官员则处于最好的职位,能保护其资产不被用于国家需求。他们的卓越地位和由此产生的极大差异,完全依赖于帝国力量的稳固。公元5世纪以后,内部冲突和外部挑战开始不断增加。公元5世纪30—70年代,罗马政府首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然后是高卢、西班牙、西西里,甚至是意大利最后也被日耳曼人的国王接管。东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试图重新夺回意大利,造成了重大的混乱,并且由于日耳曼人的再次入侵而迅速失败。地中海地区的联盟戏剧性地瓦解了位于罗马的顶级精英阶层拥有的广泛地产网络,使他们再也不能在意大利以外甚至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拥有财产。
日益加剧的政治分权,有效地消灭了西罗马上流社会的最上层阶级。这一过程始于公元5世纪地中海盆地腹地,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时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居住在罗马城内的地主拥有的地产大多被限制在拉提姆周边地区,甚至连教皇也被剥夺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教会财产。这种崩溃有助于我们理解,根据公元593年由教皇格雷戈里撰写的“对话”,为什么像主教里登普塔斯这样的一位罗马精英会认为当人们加入修道院是为了在“充满了许多灾难和各种痛苦”的世界中寻找一个避难所的时候,“凡有血肉的人的尽头已经到来”。贵族变得更加地方化,也远没有以前那么富有。衰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豪华的乡村别墅降级或废弃,到庄严的元老院不体面地消失,以及没有任何参议员家族可以追溯到7世纪早期之前的事实。教皇格雷戈里的著作也许是旧的富裕家族陷入贫穷的最深刻的例证。教会的领袖多次提到为了帮助落魄的贵族而办的一些小规模的慈善活动。一个意大利地区的前萨莫奈总督,得到了4枚金币和一些葡萄酒;一个几代人都担任过最高级别官职的贵族家族,其寡妇和孤儿也得到了微薄的捐款。 [10]
罗马超级富豪的灭亡简直令人惊叹,可以说它预示了唐朝贵族的没落:主要的区别在于,在罗马的案例中,虽然并非未知,但杀人似乎没有那么普遍。尽管如此,暴力仍然是这个过程的中心,被大量地应用于对帝国的瓜分。西罗马社会的最顶层群体的消亡注定会抑制不平等。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权利进一步下放至有产阶级中更低的层级,因为在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使是地区和次级地区的精英也消失了”。虽然新的军事精英凭借这些动荡崛起,但是在没有大规模的帝国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与罗马晚期的财富集中程度类似的事情,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至少在部分地区,农民自主权的提高甚至进一步阻碍了对当地的资源攫取。 [11]
最后的发展引出了一个问题,矫正是否不仅受顶层群体的消耗,而且受底层群体的获益的驱动?有一种证据,被认为是物质福利的替代物,即人类骨骼的残骸,它与这个概念兼容,但是由于太模糊而无法证实。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体现身体健康的指标,如身高、牙齿情况以及骨骼损伤的发生率确实有所改善。这表明普通民众的状况比他们在帝国统治时期的状况要好。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有把握地确定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在政治瓦解后人口减少和逆城市化可能减少了寄生性的负担,实际收入增加、饮食获得改善,然而同期发生的与之无关的瘟疫的流行(下一章将讨论)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12]
不同类别的考古材料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衡量资源的不平等。在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斯蒂芬研究了在罗马统治之前、之时和之后三个不同时期房屋面积的变化。房屋面积代表了和人均经济福利相关的可接受的信息:在不同文化之中,家庭收入和住宅面积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住房通常都是地位的标志。来自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英国的测量结果特别有帮助。相关数据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上,具有很高的现代学术的质量,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罗马国家的崩溃在这个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当罗马的统治在公元5世纪终止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英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多个小型的政治主体占主导地位。随着别墅被废弃、城市经济衰落,除了最基本的品种,所有的陶瓷生产都停止了,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因此大大降低:手工造型甚至都不借助制陶工人的转轮。从空间差异和一些小发现的性质来看,住所的遗址并没有反映出等级制度的真正迹象,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很少发现有丰富陪葬品的墓葬。简而言之,地方精英,如果他们真的存在过的话,并没有留下多少公元5世纪晚期和公元6世纪的历史印记。和前帝国的大部分其他地区相比,罗马时代的结构在这里被消灭得更加彻底:这个岛屿经历了无处不在的系统崩溃,而不仅仅是国家衰败。 [13]
这个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住宅结构的平均尺寸以及房屋大小差异的程度,两者都比帝国时代大幅度缩减。公元1世纪,被罗马征服后,两个指标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被逆转,这种趋势曾经提高了本地的经济产出和社会分层水平(图9.1、图9.2、图9.3)。 [14]
然而更加可惜的是,这些发现提供的数据样本和已经被研究过的罗马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存在各种缺陷,例如依赖少数几个地点或者是缺乏对某些时期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不能对住房不平等的变化做进一步的评价提供恰当的支持。即便如此,考古工作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帝国统治和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之间相互关系的机会。
虽然存在地理的局限性,这些数据显示出后帝国时期财富的分散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过程,而不是仅限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尽管我们无法对后罗马时期的总体矫正程度进行测量,国家衰败对这个富人已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环境的实际影响一定是非常显著的。崩溃造成的后果,与征服者保留了被征服国家之前的结构规模和特点的结果相比差别巨大:英格兰的诺曼底征服者保留甚至拉大了财富不平等,而被一小部分中央统治阶级剥削的辽阔领土的分裂,则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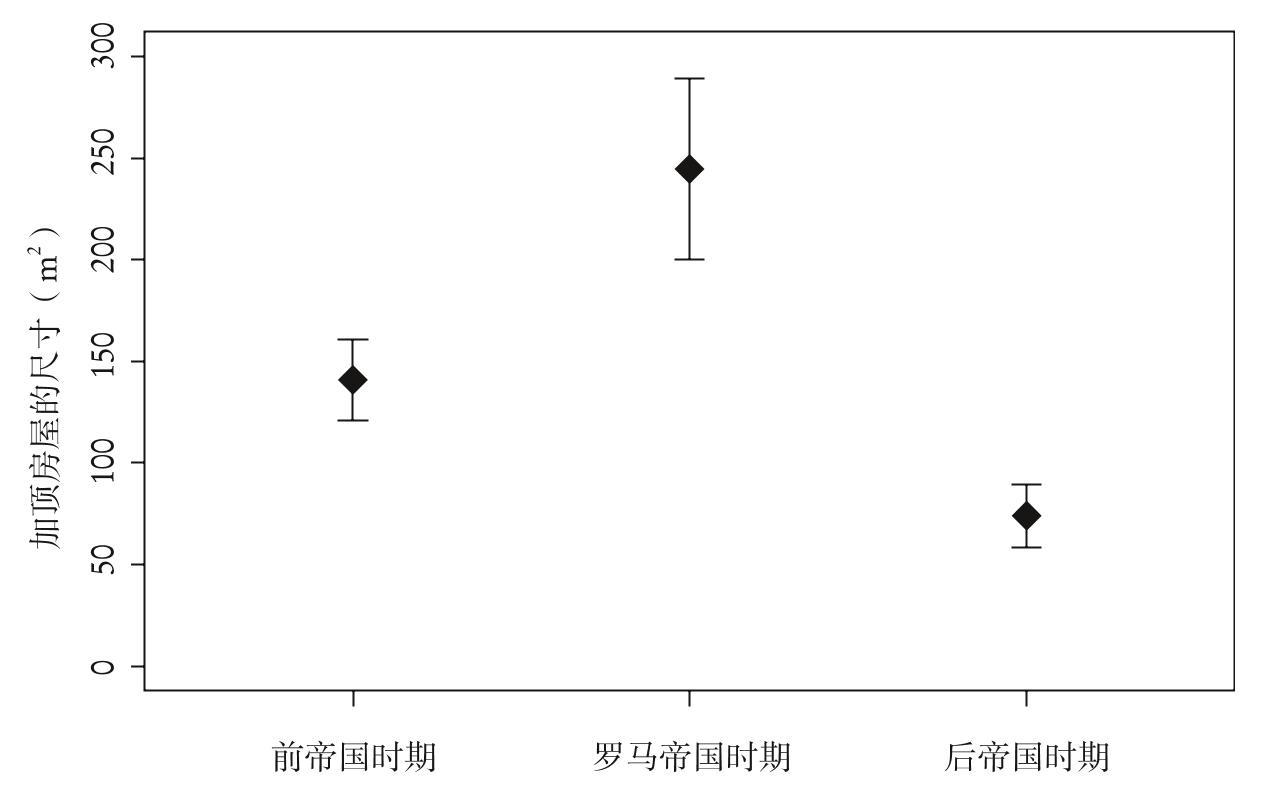
图9.1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平均尺寸(中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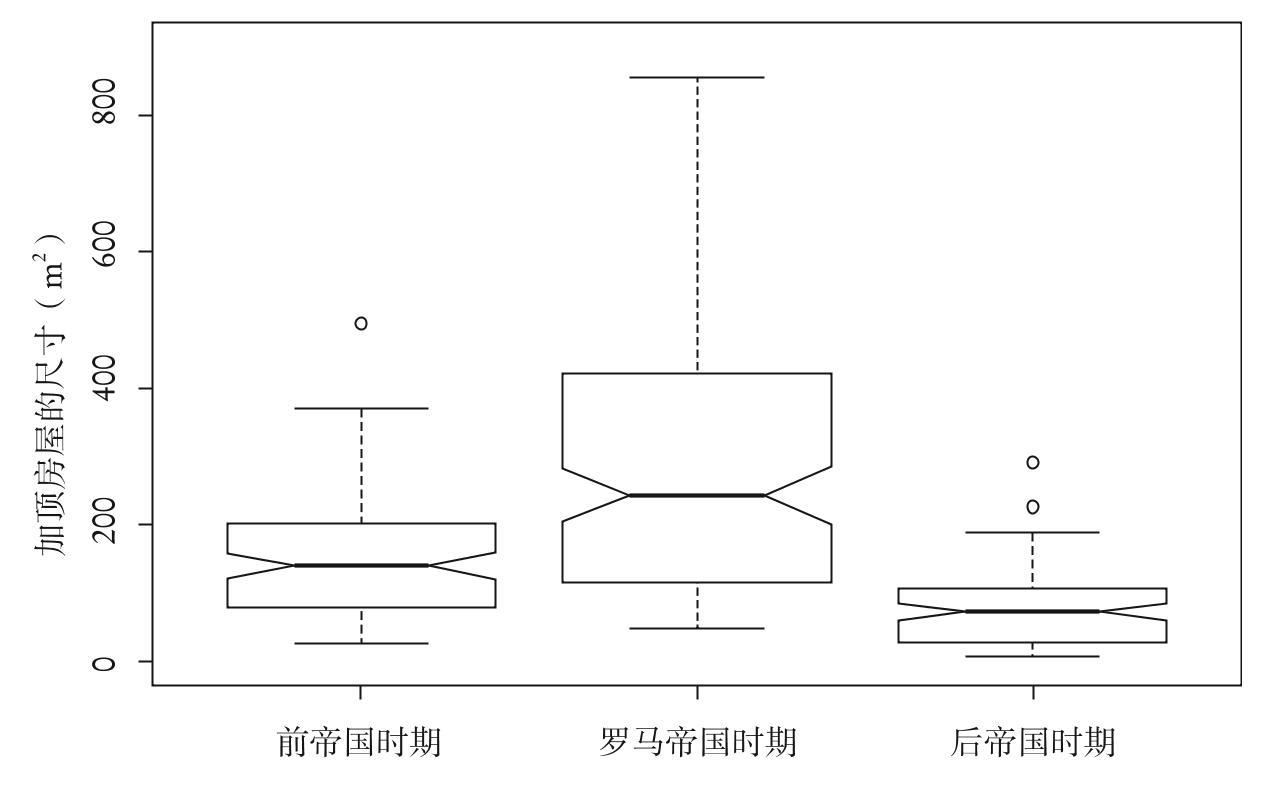
图9.2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尺寸的四分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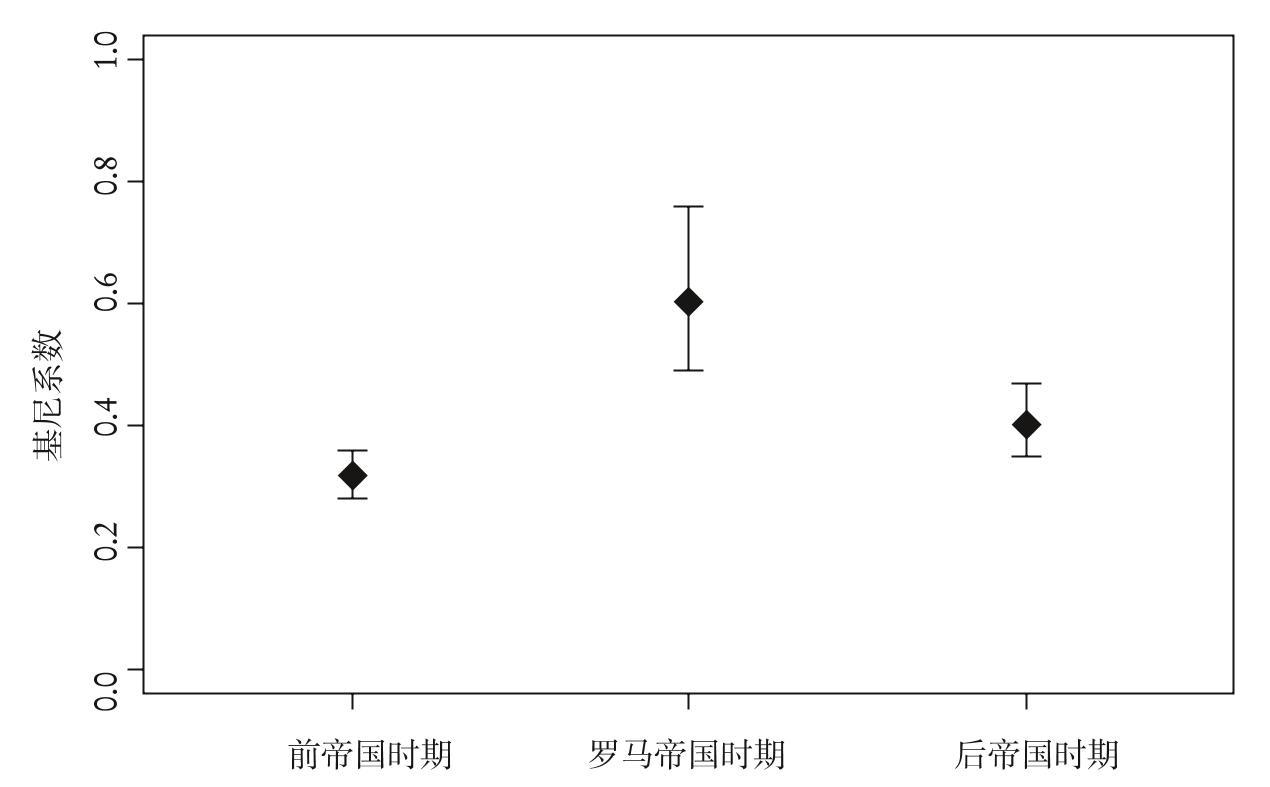
图9.3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面积的基尼系数
在公元前13世纪,通过外交、战争和贸易,地中海东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相互联系的国家体系:拉美西斯王朝统治的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正忙于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中亚述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扩张,黎凡特的城市国家也正在蓬勃发展,整个爱琴海被各个管理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大型宫殿统治。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体系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迅速崩溃了。整个地区的城市都遭到破坏或者是大规模的毁灭——包括希腊、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1200年刚刚过去,赫梯帝国就衰落了,其首都哈图沙部分被毁并且被遗弃。处于叙利亚沿海的重要城市乌加里特在几年后被摧毁,内陆的一些地区也同样如此,比如米吉多这样的城市也紧随其后。在希腊,巨大的宫殿一个一个被摧毁。有些地点已开始重建但是直到世纪末也没有完成。往南,失去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的埃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解体,被南部的底比斯祭司精英集团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各个王朝瓜分。亚述王朝同样也没能安全逃脱。在各种程度上,统治和征收机关开始分崩离析,城市消失或者以更小的规模幸存下来,书写的应用退化,帝国分裂成各种小国和城邦。产出和交换出现衰退,社会复杂程度降低。 [16]
导致这次巨大的解体的原因还存在很多争论,很多因素看起来都发挥了作用。那些所谓的“海上民族”,在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记录中都出现过的“生活在船上”的海盗团伙,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公元前1207年,尽管他们对埃及的袭击遭遇了挫败,然而30年后他们在建立起联盟后重新发动了攻击。正如拉美西斯三世所言:
在战斗中,所有的国家立刻遭到洗劫,被弄得七零八落。没有国家能抵抗得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手伸到了地球航路所能抵达的任何一块土地。
虽然法老的部队设法击败了他们,其他的社会却没有如此幸运。巴勒斯坦的菲利士人定居点有可能就是这些活动的结果,因为这里的考古遗迹发现了至少好几处可见的破坏性的痕迹。有几个地点同样显示了破坏和地震活动有关,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的“地震风暴”可能连续地袭击过这个地区。另外,有证据显示,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生过旱灾,并且转化成更大的干旱。无论这些破坏性力量在当时以何种精确的配合发挥作用,看起来各种因素正好同时发生,并且很可能并非偶然而是相互联系: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放大效应,并且摧毁了铜器时代晚期的世界体系。 [17]
爱琴海地区的崩溃尤为严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随着武士精英不断积累财富以及建立防卫中心,希腊南部大陆地区的定居点获得发展。从巨型坟墓的外观以及社会性差异化的葬品来看,社会分化也有上升。这些地方很快就建起了宫殿群。用B类线性文字和早期希腊语做记录的黏土块记载了以这些宫殿为中心,由国王和高级官员掌管的再分配经济活动。上级通过下级获得物品和服务。这种体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克里特岛南部产生的早期宫廷经济模式(被称为米诺斯文明),但是显示了更多的暴力和防卫的迹象,并且富裕的情形较不普遍。以这些大型宫殿为中心,人们在大陆地区建立了各种相当规模的王国,创造了在当今被称为迈锡尼文化的政治体系。 [18]
尽管我们对政治控制的本质和收入分配的了解比我们自身希望的少得多,然而以精英为核心的再分配中心的存在似乎很难和平均主义的观念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迈锡尼宫殿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记录在B类线性文字黏土块上的姓氏反映了少数精英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具体的个人姓名、社会地位,以及似乎被相同的几个特权家族完全控制的财富。然而黏土块几乎没有提供劳动人民使用分配的高档物品的证据。当时的两位杰出的专家曾恰如其分地说:“大量财富往上聚集,便留在上层。”只有在精英的墓穴里才能找到由金、银、象牙和琥珀制作的奢侈品。至少有一次考古材料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财富的流通变得越来越封闭,这和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上造成不平等日益上升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流通可能采取了在高等精英集团内部进行交换礼品的形式,再以进口和出口作为补充,为他们提供能够彰显地位的外国商品。 [19]
迈锡尼文明的瓦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毁灭的迹象可能和地震有关,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一些主要的地点。同一个世纪更晚时候又出现进一步的破坏,然后是新的防御工事的建设——明显遭到了军事威胁。公元前1200年紧接着的一波破坏事件,毁坏了迈锡尼、梯林斯、底比斯以及奥尔霍迈诺斯的宫殿,稍晚更是包括皮洛斯的所有宫殿。在其他地方,原因还只是基于推测:地震活动、旱灾以及流行病,加上入侵、叛乱,以及人类贸易方式和移动方式的变迁等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因为宫殿系统已无法应对发生的灾难。 [20]
在很多地方,迈锡尼文明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的早期。尽管毁坏的宫殿从来没有被重建和再利用,但是新的施工仍然时有发生,在某些地区,精英阶层还会兴盛一时。有些避难地点很容易就能守住,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公元前1100年左右,一系列新的破坏事件终结了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地区。在宫殿消失后,只有村庄得以幸存,以前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比如皮洛斯,在衰败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被保留下来,基本上是普遍被遗弃。大部分的地区没有被破坏得那么严重,“恢复到小规模的,部落存在形式”。高质量的建筑风格一去不复返,连书写都完全消失。公元前10世纪是总体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最低谷。当时希腊最大的定居点可能居住了1000~2000人,然而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小型的村庄,采取了流动性更大的生活方式。很多地点被永久废弃,国际贸易联系中断,大部分住房只能满足基本需要——只有一间屋子,坟墓的质量很差。个人墓葬成为常态,这和以前的迈锡尼时代更注重血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21]
宫殿时期的精英都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有些人也许离开后去了东方,加入了当时活跃的海盗团伙——这和2000年之后英格兰的乡绅逃离诺曼底征服者的统治类似。为了寻求保护,他们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逃到一些偏远的地点,例如一些岛屿或者沿海地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些: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消失了。汲取性的上层建筑即宫殿系统建立在农业人口身上被废除并且也没有被替代。直到公元前10世纪,可能只有最大型的或者比较大的村庄保留了一些可识别的精英阶层的痕迹。
这个时期的墓葬品的特点显示,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能够获得进口的物品。实际上,社会分化和精英财富的迹象已变得如此稀少,以至埃维亚岛的来福卡迪的一座公元前10世纪的独栋建筑竟然引起了现代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热情:这座房子150英尺 [01] 长、30英尺宽,由泥砖建成,外面有木柱包围,包含了两个墓葬,并且在其中发现了一些黄金首饰。这座在几个世纪以前司空见惯的住房是这个时期、这些地点唯一的一次突出发现。 [22]
大型建筑物、高档物品以及其他财富和地位标志物方面在铁器时代早期显而易见的稀缺与迈锡尼时期的情况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反差。不仅政治崩溃,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都衰退,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在这种环境中,对剩余进行大规模的征收和集中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即便是在强大的机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虽然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承受着巨大的艰辛,权贵却经历了更陡峭的下坠。这种大规模的系统崩溃不可能不大幅度地缩小早期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而且,即便新的精英集团在公元10世纪开始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在公元8世纪开始加速,后宫殿时期近乎普遍的贫困导致了悲惨的平等,并且很有可能为以后几个世纪希腊出现的顽强的平均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第6章讨论过的、对不平等的一个少见的约束条件。
在迈锡尼宫殿系统大规模解体的2000年后,在尤卡坦半岛南部的玛雅古典文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崩溃。到古典晚期(大约公元600—800年),国家的形成已经超越了单个城邦的形式:像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这类城市成为大型政治主体的中心,它们宣称对其他城市拥有统治权,并且利用访问、礼物交换和通婚等手段来吸引它们。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巨型建筑蓬勃发展,对庙宇和宫殿的大量投入把精英集团的物质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光辉灿烂的高度:人们发现,那个时期的奢侈品,包括进口的玉石和大理石,随处可见。在公元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地区实力出现衰退并且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被较小的政治实体取代。越来越大的政治冲突似乎和日益增长的剥削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阶级鸿沟同步发展。宫殿在城市间扩散,精英阶层得到加强,这反映在墓葬形式的变化上。人们开始更加强调血统,文化精英跨越政治界限发生融合,一切都指向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分层,以及很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不平等。 [23]
公元9世纪,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区,新的建设停止了,然后就是全面的崩溃,尽管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在尤卡坦,考古学家的发现在地理和时间上具有相当高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转变事件延续了几个世纪。然而最终,社会复杂性的丧失是普遍而严重的。在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城市蒂卡尔,建筑活动在公元830年停止,80年后可能有90%的群体被认为已经离开或者失踪。其他的主要地点同样被遗弃:最大型的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较小的定居点反而维持得更久。然而再一次地,崩溃背后的原因存在着争议。现代观点认为崩溃可能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的结果,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破坏了玛雅社会——最显著的因素是地方战争、人口压力、环境退化和干旱。 [24]
无论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绝对的规模也是有据可查。和希腊迈锡尼发生过的情况类似,拥有宫殿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交战中心并且最后退化成了小型的村庄。在南部内陆的中心地带,精致的行政大楼和住房建筑、寺庙和伫立的石碑统统都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文字和著名的玛雅历法系统。奢侈品的生产也停止了。精英机构、服务性的文化活动——例如对高贵血统的石碑崇拜等直接消失了。用一个现代权威的精辟评价来说,整个统治集团已经“随风而逝”了。 [25]
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希腊不同的是,主要的北部遗址精英文化得以幸存和繁荣发展,最有名的是公元9世纪或者10世纪末的奇琴伊察以及之后的玛雅潘和图卢姆。奇琴伊察在公元11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灾难性的衰落,受长期的干旱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文化和制度延续到公元12世纪和13世纪的玛雅潘时期。然而,在南部,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一样,大规模的解体并不局限于城市中心和统治阶级,而是吞噬了普罗大众:现代学术观点认为,其人口萎缩达到85%,数百万人的基本经济被瓦解。
这提出来一个问题,玛雅系统的崩溃对资源分配如何产生影响。国家等级制度和精英文化的物质象征全面消除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导致早期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无法保持下去。尽管平民百姓的生活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混乱的伤害,然而至少在短期内,他们也可能会因被国家精英集团施加的习惯性负担的终结而受益。更具体地说,一项研究发现,公元8世纪中叶之后,来自精英背景的放射性碳元素数量急剧下降,与此相反,来自平民背景的放射性碳的数量保持了更好的持续性,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可能经历了不成比例的消耗,尽管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最好的具体数据也许来自对尤卡坦南方低地多个地点的人类遗骸的详细调查。在古典时期晚期,精英与下属的墓葬的区别和系统性的饮食特权相关:地位较高的个人会吃得更好。在公元800年之后,这两个特征都退化了,如带有日历的象形文字这类精英产品的使用变得没有那么频繁,这意味着地位的差异和物质的不平等都被压缩了。 [26]
新世界早期的其他国家经历了类似的解体并伴随着矫正。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就够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段,墨西哥中部的特奥蒂瓦坎(现今墨西哥城的东北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6世纪或者7世纪早期,在经过了一个(由墓葬显示)社会分层日益加强的阶段后,人为的火灾摧毁了城市中心的巨大建筑。巨大的石头被搬走,雕像被破坏,碎片被扔到地上。北部和南部宫殿的地板和墙壁被烧毁,巨大的力量把公共建筑变成了碎石瓦砾。甚至一些被埋葬的骨架也会被肢解,其中的一个骨架带有显示精英地位的丰富装饰。这种行为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然而毁灭政治中心特奥蒂瓦坎的凶手身份不是很清楚:有可能在外敌入侵之前就出现了地方的动乱。这种因为不平等而针对精英和国家资产行为的意味相当明了:难以想象统治力量的系统性解体会没有伴随着控制和剥削的政治机构的解体。即使缺少文字证据,认为精英集团或多或少完好无缺地生存下来的看法和考古资料也是不相符的,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有可能已经移民或者甚至在其他的地方维持了精英的地位。 [27]
安第斯高地的蒂亚瓦纳科文明的衰落同样如此,甚至是展现系统崩溃的一个更戏剧性的案例。位于安第斯高原,临近提提卡卡湖,海拔大约13000英尺处有一个叫蒂亚瓦纳科的城市,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从公元4世纪开始扩张并持续到公元10世纪。它有着成熟的帝国形式,首都被精心设计成一个气势雄伟的仪式中心,根据宇宙学原理保持着空间对称,被巨大的护城河包围,限制进入,也让这个中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神圣的岛屿。这个封闭的区域,不仅包含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大型仪式建筑,还有大量的住宅提供给统治者和相关的精英阶层,甚至还有墓地。精英阶层的居住区,经过精心的布置和装饰,得益于精巧的水供应系统。当地的墓葬拥有丰富的墓葬品。护城河之外的房子一般没有那么奢华,即便如此,在空间走向上始终如一地执行精心规划的路线。高质量的建筑,大范围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的呈现,意味着住在里面的阶层虽然地位低于那些隐居的精英,但还是要比农村的平民富裕得多。如果拿来和后期的印加文明做对比,这些城市周边的居民有可能属于统治家族地位较低的宗亲,或者也有可能通过虚构的亲属关系和后者联系起来。因此,帝国的蒂亚瓦纳科被明确作为统治者和为其同伙服务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来建设和重建的。基于这种目的,首都的规模被限制,几万人生活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内,同时可以轻易地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据我们所知,农村的平民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和铜器时代的希腊一样,手工艺人似乎是依附于该中心,专门制作只在特权阶层范围内流通的物品。由于将权贵和普通大众在空间上进行隔离,社会经济的分层得到加强。 [28]
一些迹象表明,统治者和精英的权力在帝国的晚期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社会的不平等也增加了。然而衰退一旦开始,就会快速发展并且直到终结。像严重的干旱这类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破坏了蒂亚瓦纳科复杂的控制结构。国家崩溃了,连同它的统治者、贵族,以及仪式中心一起。首都分阶段地被遗弃,直至公元1000年被完全清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存在广泛暴力的迹象:中心东边和西边的宫殿都被摧毁了——实际上前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和特奥蒂瓦坎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些证据显示,存在故意破坏仪式建筑的行为:象征精英权力的雕塑被污损和埋葬,这通常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宗派冲突或其他暴力源头是否对这些动荡造成了影响,仍然值得探讨,并且有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等级并没有在这些动荡中保存下来。中心的衰落伴随着内陆农业的崩溃。提提卡卡湖盆地的城市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政治分裂和地方化的经济活动成为常态。人口萎缩并且撤退到易于防守的区域,居住点筑起大量防御工事用来应对暴力和不安定的情况。由于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例如对剩余的征收、专业工艺的生产)以及远距离贸易统统都失去了,旧精英也因此消失了。 [29]
在其他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崩溃如何对精英的权力和财富产生影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段,众多城市繁荣发展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整个系统在公元前1900—前1700年之间瓦解,许多地点的发展衰退或者被遗弃。再一次地,任何旧的等级和分化的制度无论如何都很难在这个过程中保存下来。 [30]
对后人来说,系统崩溃的场面往往是最显而易见的。2400多年前,雅典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荷马史诗中获得赞美的城市在他那个年代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壮观。当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经过靠近蒂卡尔和帕伦科的玛雅遗址时,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被森林覆盖,并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位于东南亚的吴哥窟遗址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直至20世纪早期才开始对主要遗址进行清理工作,还有柏威夏的圣剑寺遗址,一个面积达到10平方英里的巨大的城市,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曾经被高棉统治者偶尔当作居住地,位于一个现在完全不知名的地方的中间。当2008年我和一个同伴坐直升机访问它时,除了来自附近一个与世隔绝村子的几个保安和一条长蛇之外,我们是那里仅有的生命。 [31]
由于抹去了考古遗迹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记录,这些无所不包的系统崩溃几乎无一例外让测量同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变化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与此同时,这些灾难事件强烈暗示着大规模的收缩。系统崩溃后无论不平等和剥削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必定和高度分层的帝国政治时期的现实和典型的情况相距甚远。而且,超出前精英阶层范围的普遍贫困,也会减小征收剩余的潜力,从而降低资源不平等的天花板。考虑到带来平等化的大规模动员战争、转型革命以及灾难性传染病的特殊性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崩溃也许是我们看到的全部历史中最强大的一个矫正手段。虽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许多不为人知的案例可能已经被增加进来,但是它仍然是相当少见的,考虑到这种剧烈的变化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和痛苦,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与此相反,国家结构迅速重生往往是被外部接管的结果,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结果。转型越顺利,不平等状况就越容易被保留或恢复。
国家衰败的历史和国家存在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所谓的古王国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7世纪—前23世纪,埃及的统治者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一直都在努力地维持着国家的统一。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国家中央集权最明显的体现。分权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和公元前21世纪早期,在北部和南部出现了两个竞争性的政治势力,地方统治者获得了自治的权力。这可能对不平等状况造成复杂的影响:地方各省的统治者和贵族获得了以前要上交到中央的资源,法老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他的内部势力却衰落了——后者在国家统一的终结阶段,质量较差的朝臣坟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因为缺少更多确凿的证据以至我们难以做进一步推测,但是最顶层受到削弱至少在理论上会缩短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尾部最外端的距离。 [32]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阿卡德帝国惊人的崩溃也可能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可能规模更大。从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持续不断征战掠夺来的财富,都被交给了寺庙、皇室家族和精英集团。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的土地被阿卡德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属以及高级朝廷官员获得。由于允许各个地区积累财产,帝国财富的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探讨过这种趋势,然而其最终的失败一定会逆转这种趋势。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阿卡德帝国以一种过于戏剧化的方式出现衰落,传说是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引起了一个神圣的“咒语”的诅咒(本小节标题中引用的句子就出自关键的叙述)。实际的原因其实更普通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加上外国的压力和干旱,动摇了阿卡德帝国的根基,苏美尔人和其他的地方政治势力重新独立,城市的疆域出现急剧的收缩。最上层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必然会逐渐减少。 [33]
通常情况下,这种收缩只是暂时的,新的帝国势力会捡起碎片直至又屈服于新的分裂者或征服者。在有着法老的埃及,“中间阶段”的分裂总是会迎来再次统一。从公元前22世纪—前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被乌尔(学界称为“乌尔三世”)、巴比伦(汉谟拉比及后来的卡西特)以及米坦尼的连续王国,以及数次改朝换代的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统治。再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当玛瑞——一支位于当代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附近幼发拉底河的中等势力,在公元前1759年被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摧毁时,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在它从前的一个次级中心特卡建立起了一个新王国哈纳,有效地利用了玛瑞从前的疆域,并且从巴比伦独立出来。 [34]
相比之下,和上一节讨论过的那种大规模的崩溃比,这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那些新生力量能够快速崛起并进行接管的地区。帝国分裂成几个较小的政治单位,给顶层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造成下降的压力,即使它远远算不上与更全面的崩溃形式相关的大规模矫正。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棘手的挑战: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能够记录或者测量经济差距的缩减程度。然而,我们不能选择放弃或者忽视——原因很简单,相比拥有更好记录的近代或者现代社会,早期社会更有可能经历间歇性的国家衰败和权力分散。无视国家衰败内在的平等化潜力,就会忽视一种强有力的矫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是朝着这个方向,搜寻发出信号的替代数据,无论这些信号多么模糊不清。
我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大约在公元前1069年,经历了前面所讲的铜器时代晚期的危机后,埃及被有效地划分成位于南方的上埃及(处于底比斯的阿门神高级祭司控制之下),以及位于北方的下埃及(以塔尼斯作为中心)。利比亚军事力量的流入造成北方进一步分散。几个自治的地区性权力基地在公元前10世纪的部分时间,尤其是自公元前9世纪晚期起(这个时期通常有21~23个朝代)为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这种权力下移的过程挤压了地方精英的购买力,因为后者依赖于国家收入,与国家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来源以及来自和国家统一相关的私人资产或者经济活动的收入。萨卡拉的一个墓地,为旧都孟菲斯市的一个主要墓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相对的贫困化。这些发现来自第19代王朝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表兄弟蒂亚墓穴的一个副井,第19代王朝是公元前13世纪埃及帝国荣耀的鼎盛时期;这个副井属于蒂亚的秘书卢如德夫。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这个副井和它的内室装满了棺材和葬品。这里一共埋葬了74人,有一些装在棺材里面,有一些只是用垫子包裹着,还有一些根本就未入殓。棺材质量普遍很差:一些迹象显示曾经有盗墓者进入,但是他们似乎很快就放弃了,也许是对这一堆外表不堪的东西感到气馁。和同一时期埃及南部的棺材相比,这些棺材的做工明显要差一些:它们是用小块的木材拼凑而成,只是在关键的部位才有装饰。只有少部分有字迹,且多数要么是假的——由无意义的伪象形文字组成,要么已经腐烂到无法辨认。 [35]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在中埃及其他几个地点,出土了一些同样粗制滥造刻有伪象形文字的棺木和只剩下木乃伊残骸的墓葬,时间大约为同一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国家中,这些墓葬反映的还是精英的实际状况,因为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以使用近似人形的木质棺材,虽然棺材的质量很差。这可以当作环境证据,证明和更稳定的南方地区相比,孟菲斯地区上流阶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出现了下降。在那个时代北方最大的中心坦尼斯的皇家陵墓,人们甚至发现了旧物品,包括礼器、珠宝和石棺等被广泛重复使用的情况。 [36]
在当时的底比斯南部的精英阶层中间,棺材的再利用也变得很普遍。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精英阶层无力购买新的棺木,不如说是因为离开北部后原材料变得稀缺。并且,最重要的是,对猖獗的盗墓行为的担忧导致他们避免使用昂贵的可以被剥离的棺材部件,比如镀金,以及更重视对尸体进行细致的防腐处理——这是一项使其免于受到肉食动物的侵害的投资。从醒目的墓葬祭司礼堂向秘密的组团式墓群的转变同样支持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发现原始的证据来证明底比斯精英的贫困,考虑到这个由阿门神的祭司领导的集团不仅控制了埃及的一大部分,而且抢夺了以前的皇家陵墓里的财宝,因此他们并不缺少收入来源。在这方面,他们和北方的贵族不同,北方地区由于出现了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精英阶层的收入和支出受到抑制,严重依赖精英阶层消费能力的专业工艺技能因此被削弱。 [37]
我选择这个例子来说明在有限的国家衰败的环境中识别矫正迹象的困难。全面的系统崩溃通常能提供考古学的证据,用来证明收入和财富差距受到侵蚀。相比之下,不太明显的混乱,在经常是零星的和模棱两可的代替数据里,并不能留下类似的坚实的痕迹。在这些情况下,别说要测量不平等的总体缩减,即使是寻找精英财富变化趋势的任何尝试,必然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通常无法超越猜想的程度。这里还涉及一些严重的解释性问题,最明显的是已经大量讨论过的把丧葬习俗和其他储存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的风险,以及凭借特定发现进行归纳的做法是否合理的问题。对来自埃及第三中间时期的墓葬材料的思考,把我们带到了(也许能够超越)对不平等的研究能够推进到的极限。由政治分裂驱动的矫正多发生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现象,对现代观察者来说,其大部分将永远地被掩盖。在不平等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暗物质”,几乎可以确定其存在但是难以准确定位。
很多历史证据的局限性无论多么严重,都会给我们的论点提供支持——前现代掠夺型国家的暴力解体,由于剥夺了原有精英的财产和权力,会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历史中,或者说,在当今的世界,是否还能看到这种矫正方式?乍一看,答案有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在第6章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更倾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不平等程度。虽然这些冲突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力,但很少出现国家治理的崩溃或者整体社会经济规模缩减的情况,我刚刚讨论过的一些戏剧性的前现代案例就是证据。
然而,当代有一些至少有可能更接近的案例。东部非洲的索马里通常被认为是最近出现的国家崩溃的最重要的例子。当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政权在1991年被推翻后,国家分裂成多个对立的派别和地区,并且一直缺少最顶层的政府机构。在北方出现了索马里兰和邦特兰这样的“国家”,其余的地区则断断续续地由军阀、民兵(包括“圣战”组织“青年党”)或者来自周边国家的部队控制。只是在最近几年,名义上的联邦政府开始对摩加迪沙进行控制。
人民的福利水平普遍很低。一项对阿拉伯国家(广义的)贫困的研究基于儿童死亡率、营养、入学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这些因素,将索马里排在最后一位。由于严重缺乏数据,最近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包含在内——除了在一个多维的贫困指数排名中,索马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得分第六低的国家。它还是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比例第六高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索马里是如此的“破败”,正如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在一次访谈中所说。 [38]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衰落和国家的分裂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由于证据不足,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必然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采取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背景下进行观察时,多个指标显示,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不平等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
出现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结果的原因在于,到1991年的时候,环境已经极度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居民。在1969—1991年的西亚德·巴雷统治时期,采矿业的收益由独裁者及其盟友独占是政府唯一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尽管最初实行的政策是无宗派主义政策,巴雷最终还是偏向自己的家族和支持他的人,同时残暴地对待其他人,把他们当作榨取的对象。对对立群体采取暴力手段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土地改革使政客和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商人从中获益。政府官员及其亲信剥离他们资产的国有化业务,汲取大量的公共开支,而公共开支的90%最终流向行政机关和军队。来源于“冷战”对抗和难民控制的外国援助都转移到了执政者手上。
即使是按照这个地区不令人羡慕的标准,腐败也是极为严重的。高级官员和巴雷家族洗劫了最大银行的储备,最终导致银行破产。唯一的国有银行为了迎合在政治上互相关联的精英集团的需要,故意高估索马里货币,使购买进口货的富裕的消费者获益,出口货物(比如肉类)的穷人则受到伤害。经营着一个“看门人国家”,巴雷政权控制了这个国家财富的流入和流出。总而言之,这些邪恶的干预在摩加迪沙内部以及在首都和其他地区之间制造了不平等。这一政权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极少。因此,即使在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公共物品大部分还是要由非正规部门以及地方机构或团体,比如家族网络提供。占劳动力大多数的牧民被忽视并且受到最严重的剥削,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公共资金。 [39]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的失落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分裂甚至减少了暴力,尤其在外国军队撤出的1995年至埃塞俄比亚入侵的2006年间:暴力冲突集中在1990—1995年,此时国家开始实质性的解体,2006—2009年,努力重建它的势头首次聚集。尽管也会有军阀和民兵组织向平民收取租金,然而由于受到规模和竞争的限制,平民的负担比独裁时期要低得多,税、贸易和商业面临的障碍比以前少很多。因此,按多个测度标准对比西非国家的生活水平,索马里曾多次超越或者赶上两个接壤的国家。在国家崩溃后,大部分发展指标都改善了,仅有的例外是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是由于接受的外国援助减少而非政府服务出现了变化。一次对索马里和41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13项发展指标的比较显示,在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年,尽管索马里在全部有记录的指标中的排名都很糟糕,然而现在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明显相对于许多其他的国家,索马里都取得了进步。在对大约同一时间经历战争或经历和平的国家进行比较时,情况就是如此。 [40]
可以预期的是,有两个因素压低了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的不平等水平:(1)国家统一时期从地租中获益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精英消失了;(2)歧视农村人口、偏向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政策被取消。无论如何,还是有极少的现实数据与这种预期一致。1997年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低于同期的邻国(0.47)以及西非国家(0.45)。标准化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记录了索马里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早期出现了下降,尽管不确定性的范围很大。我们很难知道,应该给最近估计的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3~0.46的结果多大的权重,和1997年不同的是,其缺少中央政府的治理。考虑到证据的性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其他福利指标的改善和一个腐败和残暴的政府的灭亡是相关的:巴雷时代的索马里,政府实际上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国家崩溃带来的矫正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即便如此,索马里的例子至少为本章的总体观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41]
巴雷统治下的索马里的经验具有更广泛的价值。和现代的西方社会相比,不发达世界中的掠夺型或者“吸血鬼”型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统治传统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它是高水平的精英掠夺和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应的结合体。可以确定的是,有多个事项需要注意。前现代国家普遍没有受到索马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限制了给它们国民造成的伤害的大小。而且,这也是我对掠夺型国家所做的“托尔斯泰式”定义所必需的,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它们和前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没有四海皆准的原理。然而,很容易看出,一个贪婪的国家的终结,如何为人类整体的福利(特别是在不平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无论多少居民宁愿有令人憎恶的政府而不是没有政府。有一个经济模型显示,一个肆无忌惮的掠夺型政府有可能比无政府状态更加不利于大众获得福利。 [42]
在某些情况下,崩溃使每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从而影响到不平等状况——但是富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整体复杂性大幅度下降,就像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后古典时期的尤卡坦,或者后蒂瓦纳科时期提提卡卡盆地最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中断更可能仅限于政治领域,就像最近的索马里的情况,矫正并不一定和生活水准的广泛下降相关,而更多的是通过影响顶层集团来实现的。安全的环境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国家衰败造成的分配结果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它是否将民众暴露在外来的侵略性掠夺之下(例如草原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的入侵),或者影响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尽管矫正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总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国家的等级制度和压榨机构的暴力性终结会造成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国家和文明的崩溃代表着不平等矫正世界史的第三个,也是最古老、游历最广的末日骑士:他能够把不平等踩于脚下,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
[1] Rotberg 2003: 5–10 lists features of state failure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For the nature and limitations of premodern states, see Scheidel 2013: 16–26.Tilly 1992: 96–99 identifies essential state functions with model clarity.
[2] Tainter 1988: 4 (quote), 19–20.For historical examples, several of which are covered in this chapter, see 5–18.
[3] Renfrew 1979: 483.
[4] Tang land schemes: Lewis 2009b: 48–50, 56, 67, 123–125; cf.also Lewis 2009a: 138–140 for earlier equalfield schemes.Quote: Lewis 2009b: 123.Aristocracy: Tackett 2014: 236–238(quote: 238).
[5] Huang Chao: Tackett 2014: 189–206.Quotes: 201–203.
[6] Tackett 2014: 208–215 (quote: 209–210).
[7] Epitaphs: Tackett 2014: 236; 225 fig.5.3: their frequency fell from about 150–200 per decade in the period from 800 to 880 to 9 per decade during the following four decades.Changeover: 231–234.
[8] 在一个精英阶层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治权力的行使中获得收益的社会,国家衰败将会比那些只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战争更严重地影响精英阶层。The effect of the U.S.Civil War on the Southern states provides an example of moderate leveling in the latter scenario: see herein, chapter 6, pp.174–180.
[9] Wickham 2005: 155–168 is the best analysis; see herein, chapter 2, pp.78–79.Ammianus 27.11.1 (quote).Holdings: Life of Melania 11, 19, 20
[10] Breakdown: Wickham 2005: 203–209 .Quotes: Gregory the Great, Dialogues 3.38.Papal charity: Brown 1984: 31–32; cf.Wickham 2005: 205.
[11] Brown 1984: 32 (violence); Wickham 2005: 255–257 (quote: 255), 535–550, 828.
[12] Koepke and Baten 2005: 76–77; Giannecchini and Moggi-Cecchi 2008: 290; Barbiera and Dalla Zuanna 2009: 375.For the varied challenges of interpreting body height, see Steckel 2009: 8.For height inequality, see Boix and Rosenbluth 2014, and cf.herein, chapter 1, p.59.
[13] House sizes: Stephan 2013.Cf.Abul-Magd 2002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 sizes in Amarna (New Kingdom Egypt), and Smith et al.2014 and Olson and Smith 2016 for inequality in pre-Columbian Mesoamerican house sizes and furnishings.Britain: Esmonde Cleary 1989; Wickham 2005: 306–333, esp.306–314.
[14] Reproduced from Stephan 2013: 86–87, 90.
[15] See Stephan 2013: 131 (Italy), 176 (North Africa); but note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residential structures in North Africa is also lower for the post-Roman than for the Roman period: 182.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case study provides an instructive counterpoint to developments in ancient Greece, where economic growth and expanding house sizes did not coincide with greater variation, arguably thanks to a different set of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norms: see herein, chapter 6, p.198.For post-Roman leveling, see herein,chapter 3, p.88; for the Norman conquest, herein, chapter 6, pp.200–201.
[16] Cline 2014: 102–138 provides the most recent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or this collapse.
[17] Cline 2014: 139–170 and Knapp and Manning 2015 review various factors.See esp.Cline 2014: 2–3 (quote), 1–11, 154–160 (destruction), 140–142 (earthquakes), 143–147 (drought),165, 173; and Morris 2010: 215–225 (collapse).
[18] On the early phase of Mycenaean culture, see Wright 2008, esp.238–239, 243–244, 246.
[19] Galaty and Parkinson 2007: 7–13; Cherry and Davis 2007: 122 (quote); Schepartz, MillerAntonio, and Murphy 2009: 161–163.In one center, Pylos, skeletons recovered from wealthier graves even display better dental health: 170 (Pylos).
[20] Galaty and Parkinson 2007: 14–15; Deger-Jalkotzy 2008: 387–388, 390–392.
[21] Final phase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 Deger-Jalkotzy 2008: 394–397.Temporary elite survival: Middleton 2010: 97, 101.For conditions in the post-Mycenaean period, see Morris 2000: 195–256; Galaty and Parkinson 2007: 15; Middleton 2010.
[0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2] Fate of the elite: Galaty and Parkinson 2007: 15; Middleton 2010: 74.Imports: Murray 2013: 462–464.Lefkandi: Morris 2000: 218–228.
[23] Willey and Shimkin 1973: 459, and cf.484–487; Culbert 1988: 73, 76; Coe 2005: 238–239.Coe 2005: 111–160 gives a general survey of this period.
[24] Maya collapse, see Culbert 1973, 1988; Tainter 1988: 152–178; Blanton et al.1993: 187;Demarest, Rice, and Rice 2004b; Coe 2005: 161–176; Demarest 2006: 145–166.Variation:Demarest, Rice, and Rice 2004a.Causes: Willey and Shimkin 1973: 490–491; Culbert 1988:75–76; Coe 2005: 162–163; Diamond 2005: 157–177; Kennett et al.2012; cf also Middleton 2010: 28.
[25] Coe 2005: 162–163 (quote: 162); also Tainter 1988: 167: “The elite class ...ceased to exist.”
[26] Decline of Chichen Itza: Hoggarth et al.2016.Mayapan: Masson and Peraza Lope 2014.Commoners: Tainter 1988: 167; Blanton et al.1993: 189.Relief: Tainter 1988: 175–176.Dates: Sidrys and Berger 1979, with criticism in Culbert 1988: 87–88; Tainter 1988: 167–168.Burials and diet: Wright 2006: 203–206.Calendar dates: Kennett et al.2012.
[27] Millon 1988: 151–156.Cowgill 2015: 233–239 speculates about the role of intermediate elites who may have weakened the state by taking over resource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available to the authorities (236–237).Elite émigrés ma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rise of regional centers following the fall of Teotihuacan.
[28] Kolata 1993: 104, 117–118, 152–159, 165–169, 172–176, 200–205.
[29] Inequality: Janusek 2004: 225–226.For the collapse, see Kolata 1993: 282–302; Janusek 2004: 249–273.Specifics: Kolata 1993: 269, 299; Janusek 2004: 251, 253–257.
[30] Wright 2010, esp.308–338 for decline and transformation; and see 117 for size variation among urban houses.
[31] Thucydides 1.10; Diamond 2005: 175 (Cortés); Coe 2003: 195–224 (collaps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
[32] 参见Adams 1988:30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政治主体的笔记。其属于历史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无论这些国家最初是防御型的还是掠夺型的,是城市型的还是地域更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没有可能永久性地克服物质和社会环境施加在它们身上的脆弱性”。Egypt: Kemp 1983: 112.
[33] “Empire”: Scheidel 2013: 27, summarizing existing definitions.Curse and quote: The Cursing of Agade, Old Babylonian version 245–255 (“The electronic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 http://etcsl.orinst.ox.ac .uk/section2/tr215.htm).Kuhrt 1995: 44–55, esp.52,55, offers a précis of Akkadian history and its ending.See also herein, chapter 1, pp.56–57.
[34] Kuhrt 1995: 115.
[35] Saqqara: Raven 1991: 13, 15–16, 23, and the catalog 23–31 with Plates 13–36; see now also Raven forthcoming.For the date, see Raven 1991: 17–23; Raven et al.1998.
[36] Middle Egypt: Raven 1991: 23.Tanis: Raven et al.1998: 12.
[37] Thebes: Cooney 2011, esp.20, 28, 32, 37.
[38] Nawar 2013: 11–1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180–181 (and cf.163 for the lack of an overall index score);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may/08/ayaan-hirsi-aliinterview.
[39] Clarke and Gosende 2003: 135–139; Leeson 2007: 692–694; Adam 2008: 62; Powell et al.2008: 658–659; Kapteijns 2013: 77–79, 93.Hashim 1997: 75–122; Adam 2008: 7–79;Kapteijns 2013: 75–130 offer general accounts of Barre’s rule.
[40] Nenova and Harford 2005; Leeson 2007: 695–701; Powell et al.2008: 661–665.Cf.already Mubarak 1997 for Somalia’s postcollapse economic resilience.
[41] Inequality: Nenova and Harford 2005: 1; SWIID;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4.I paraphrase from President Ronald Reaga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of January 20, 1981,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42] Public goods: Blanton and Fargher 2008, a pioneering global cross-cultural survey.Model: Moselle and Polak 2001.
至此,我们集中讨论了人对人的暴力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大规模的动员战争鼓励了群众的讨价还价同时榨取富人;血染的革命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以及作为贵族的那“1%”;整个国家的崩溃铲除了那些曾极尽其能事搜刮并藏匿一切可得剩余的富有精英。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又一个矫正手段——第四骑士传染病。与其他三个骑士不同的是,它涉及其他物种,从而无须诉诸暴力,尽管有些细菌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攻击几乎比任何人为灾难更致命。
传染病如何减少不平等?它们以一种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在其1798年的《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一书中称为“现实性抑制”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马尔萨斯的思想根植于这样一个假设:长期来看,人口要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这反过来又阻止了人口进一步增长:通过“道德约束”抑制生育的“预防性抑制”——延迟婚姻和生育,以及提高死亡率的“现实性抑制”。用马尔萨斯自己的话来说,这些现实性抑制:
每一个……在任何程度上导致人类寿命的自然过程缩短的原因包括……一切有害身体的职业,过度的劳动以及季节变化的影响,极端贫困,糟糕的儿童养育,大城镇病,凡此种种,加上一连串的常见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灾害和饥荒。 [1]
在这个包罗一切的陈述中,这些“现实性抑制”手段,将人口压力的直接后果,与无须由人口因素引起(即使是人口因素也不会加重),完全外生于自然的传染病等事件联系起来。现代研究强调通过提高生产率应对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的重要性。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有助于避免马尔萨斯陷阱。因此,最复杂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型设想人口和生产在稀缺性压力和技术或制度进步之间的权衡中发展时会出现一种棘轮效应。此外,在过去150年中,人口转型被认为通过爆炸式的创新与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条件下的生育水平下降相结合,缓解了马尔萨斯约束。生育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于以前世代的特征。由于这个原因,马尔萨斯机制主要与我们对前现代社会的理解有关,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对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英国而言,最好的可得证据充分表明,无论生活条件如何,致命性传染病的广泛传播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外源性因素,尽管它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流行病暴发,甚至如果流行病恰好在资源紧张的时期暴发,可能会加剧流行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 [2]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瘟疫通过改变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矫正(不平等):降低前者的价值(如地价、租金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并提高后者的价值(如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地租)。这使得富裕的地主和雇主相对以前更少一些,劳工相对以前生活得更好一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降低了。同时,人口变化也与制度发生相互作用,决定价格和收入的实际变化。工人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同,传染病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土地,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定价的可能性是成功矫正的基本前提条件。细菌和市场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抑制不平等。
最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除极少数情况,任何所发生的矫正都不会持久,其效果最终被重生的人口压力产生的人口统计因素的反弹效果抵消。
在14世纪2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刻,瘟疫在戈壁沙漠突然暴发,并开始向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蔓延。瘟疫是由一种叫鼠疫菌的细菌引起的,该细菌寄生于跳蚤的消化道中。鼠类跳蚤是最常见的宿主,已知数十种啮齿类动物可以携带感染瘟疫的跳蚤。通常,那些跳蚤更喜欢寄生于啮齿动物身上,只有当原始的宿主衰竭时它们才寻求新的宿主:这是人类感染瘟疫的原因。鼠疫有三个变种,其中腺鼠疫最为常见。它因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显著肿大而闻名——跳蚤通常会咬这些部位,但这类鼠疫得名于因皮下出血而导致的充血性腹股沟淋巴结炎。感染这类鼠疫的结果是细胞坏死以及神经系统麻痹,50%~60%的感染者会在感染后的几天内死去。第二个变种是肺鼠疫,它更致命,通过感染者肺部呼出的微粒在空气中的传播直接传染给其他人。死亡率接近100%。第三个变种是败血症型鼠疫,它很罕见,它的病原体在昆虫中传播,传播非常迅速,并且无药可治。 [3]
14世纪第二个25年,鼠类携带着感染了病菌的跳蚤向东扩散至中国,向南到达印度,向西传播到中东、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中亚的商队路线成为瘟疫传播路线。1345年,这场瘟疫传播至克里米亚半岛,意大利商船上的人被感染后又把它从这里携带至地中海地区。现代研究把这个过程追溯到对克里米亚的卡法地区热那亚人聚居地的围攻:当瘟疫在围攻这个城镇的鞑靼人中暴发时,据称,他们的首领札尼别命令将感染瘟疫的尸体用抛射器射入城内以传染城中的热那亚人。然而,这没有必要,甚至是无用的。因为腺鼠疫和肺鼠疫病毒各自的宿主(啮齿动物和人)是活体时才能传播瘟疫。活动中的商业联系足以保证啮齿动物和跳蚤在城里城外的移动了。 [4]
瘟疫在1347年末袭击了君士坦丁堡。那位退位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尊对病症的准确描述被保留了下来:
没有任何医生精于此道。这种疾病的传染方式不一。无法抵抗这种疾病的人在同一天死亡,其中一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那些可以抵抗两三天的人起初烧得非常严重,于是,疾病就开始攻击头部……在另一些人中,病魔攻击的不是头部,而是肺部。用不了多长时间,肺部就感染炎症,使胸腔产生剧烈的疼痛。病人呕出带血的痰液,呼出的气体恶心发臭,喉咙和舌头因发热而变干,发黑和呈充血状……其上臂和下臂长出了脓疮,有些人的脓疮长在下颌部位,另一些人则是其他部位……黑色的水疱出现了。有些人身上长满了黑点,有些人身上很少但很明显;另一些人的黑点模糊却很密集。病人腿部或手臂上长出了巨大的脓疮,切开它后,大量恶臭的脓液从中流出……一旦人们觉察到已经染病,那就回天乏术,只剩绝望了,这使其更加虚弱,病情愈加恶化,离死也就不远了。 [5]
携带致命病毒的货物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后,瘟疫便在1348年袭击了阿拉伯的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突尼斯等大城市。到第二年,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被这一传染病吞噬,损失巨大,城市中心尤甚。
再往西,1347年秋天离开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的船只将瘟疫传播到西西里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蔓延到南欧大部分地区。比萨、热那亚、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与许多较小的城镇一样,十室九空。疫情于1348年1月传播到马赛,迅速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肆虐。瘟疫向北的扩散畅通无阻:1348年春天,巴黎遭难,继而是法兰德斯和低地国家。1349年斯堪的纳维亚出现疫情,从这里,瘟疫甚至传播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边远乡村。1348年秋天,瘟疫通过其南部港口进入英国,并在第二年登陆爱尔兰。德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尽管不如欧洲其他地区严重。 [6]
同时代观察家诉说着关于疾病、痛苦和死亡的令人悲痛欲绝的故事——无法顾及丧葬习俗,充斥着普遍的无序和绝望。都市作家都将描写主要城市的遭遇放在首位。阿尼奥洛·迪·图拉留下了关于锡耶纳遭受瘟疫后景象的触目惊心的描述,他自己的不幸让人更加痛苦:
锡耶纳在5月开始出现大规模死亡。这是一件残酷而可怕的事情,对其中的残酷和无情之处,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几乎每个人都被目睹的痛苦吓傻了。人类的言语简直无法再现这种恐怖的事实。确实,只要没有看到这可怕一幕的人都能说是被上天眷顾的。患者几乎立即死亡。他们的腋窝下和腹股沟部位会肿大,说话间就突然倒下了。父弃子、妻离夫、手足分离,因为这种疾病似乎闻一闻、看一看都会被感染。他们就这样死了。无论是金钱还是友谊都无法让人埋葬死者。家人最多只能将死者放入壕沟,没有神父,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送葬钟声。锡耶纳的许多地方都挖了很深的坑,里面尸体堆积如山。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不分昼夜,死者全都被扔在那些沟渠里,并用泥土覆盖。填满一个挖一个。而我,阿尼奥洛·迪·图拉……亲手埋葬了我的5个孩子……这么多人死亡,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认为,末日来临了。 [7]
阿尼奥洛·迪·图拉提到的万人坑也见于其他人的描述中,从中你可以想象大批生命同时消亡的场景。乔万尼·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瘟疫有着经典的描述:
尸横遍野……没有充足的墓地来安葬死者……所以在墓穴用光后,只能在教堂的院子里挖出一条条巨沟来堆放尸体。成百上千的尸体像船运货物一样被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每一层覆盖上一薄层泥土,直至巨沟被填满。
这些描述已经被在欧洲不同地区发现的万人坑证实,有时还有瘟疫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据。 [8]
中世纪大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地区遭受的毁灭则乏人问津。薄伽丘不得不提醒读者:
在零星分布的小村庄和乡村领地,没有任何医生或仆人可以帮助穷苦不幸的农民和家属。这些人随时可能倒在路边、田地里、自家小木屋中,就像动物一样死去。 [9]
到1350年时,瘟疫已经在地中海地区肆虐,到第二年整个欧洲的疫情开始趋于平缓——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中世纪瘟疫的见证者曾费劲而徒劳地测算那些无法测算的数据,最后不得不止步于大概的或某种典型的说法。重新计算这些人提供的伤亡人数毫无意义。即使如此,1351年为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计算的2384万瘟疫死亡人数结果也未必就是不可靠的。死亡率的现代估计在25%~45%之间。根据保罗·马拉尼马所做的最新估计,欧洲人口从1300年的9400万下降到1400年的6800万,下降了1/4以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损失最为严重。它们的人口在瘟疫前接近600万,瘟疫造成了差不多一半人的死亡,直到18世纪早期才达到瘟疫前的水平。意大利则至少有1/3的人丧生。中东死亡人数的可靠估计很难获得,但埃及或叙利亚的死亡率通常在可比的水平,尤其是考虑了直到15世纪初的总损失后。 [10]
无须详谈,黑死病影响之巨大毫无疑问。正如伊本·赫勒敦在他的世界历史中写道:
东西方的文明都遭到破坏性的瘟疫的蹂躏,国家荒芜,人口大量死亡……整个人类世界面目全非。
确实如此。瘟疫期间及之后的数年,人类活动减少。从长远来看,瘟疫及其造成的混乱对人们各方面的态度和广泛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影响:教会权威减弱,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同时兴起;由于恐惧情绪的蔓延和继承人的死亡,慈善活动也增加了;甚至艺术风格都受到影响,医学从业者被迫重新考虑长期以来被珍视的原则。 [11]
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在黑死病之前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人口已经出现巨大增长——增长到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从公元1000年以来,在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和农作物改良、政治不稳定减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定居点、产出和人口都扩张了。城市规模变大,数量也增多了。然而到13世纪后期,这一持续很久的繁荣景象便终结了。当“中世纪气候最佳期”结束时,生产力也下降,数不清的饥饿的嘴推高了食品价格,需求开始超过供给。然而耕地不再增加,牧场萎缩,这本身导致了蛋白质供应量的减少,更何况基本的谷物变成越来越不足的、在食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食。人口压力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实际收入。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已属万幸。14世纪初,不稳定的天气条件造成的歉收导致灾难性的大饥荒,情况进一步恶化。尽管这个世纪前1/4时间里人口数量已有所降低,但生存危机仍持续了又一代人的时间。祸不单行,动物传染病几乎使家畜消失。 [12]
看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某种形式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陷阱中,内生性问题,如由先前的人口增长和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和以令产出降低的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外部冲击,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生活变得窘迫,但这有利于控制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精英阶层。黑死病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却未影响物质基础设施。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量下降幅度小于人口下降幅度,导致人均产出和收入上升。不管瘟疫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更多地杀死了劳动力人口而不是老人或者小孩,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确实变得更加丰富了。地租和利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工资,都下降了。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劳动者有望获益。然而,这个过程如何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这些中世纪劳动者有效议价能力的制度和权力结构。
西欧同时代的观察者很快就注意到高死亡率带来的工资上升现象。加尔罗默修会的修道士让·德·韦内特在其编年记录中记载了大约1360年(紧随瘟疫肆虐之后)的情况:
尽管一切都很充足,但所有东西的价格都翻番了:家庭设备和食品以及商品,雇工,农场工人和仆人。唯一的例外是土地产权和房屋,这两者在当下供过于求。
根据罗彻斯特修道院的威廉·德内所作编年记录:
劳工短缺随之而来,底层人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扬眉吐气,三倍于以往的工资也很少能吸引其为上流社会效劳。 [13]
雇主迫不及待地给当局施压以遏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黑死病降临英格兰不到一年,在1349年6月,国王便通过了《劳动者条例》:
由于大量人口,尤其是工人和受雇者(“仆人”)已经在这次瘟疫中死亡,很多人观察到主人的需要和雇员短缺的情况后拒绝工作,除非他们能得到额外的薪水……我们已经发布法令,英格兰王国境内的人,无论男女,是否自由之身,只要身体健康且不满60岁,除非是从事贸易、经营某类手艺、有自耕地需要耕作或已受雇于人,如果被提供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就业机会,有义务接受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且只能被支付合理的报酬,即只能被支付与其在本王统治的第二十年(1346年)时其所在地区工作得到的通常的收入,或者五六年前的某一合理年份的收入……任何人不应支付或承诺高于以上定义水平的报酬,若违反本法令,将处以其支付金额或允诺支付金额两倍的罚款……工匠和工人不应该凭借其劳务和手艺获得比上述年份和在所工作地他们曾经获得的酬劳更多的薪水;如果有人拿了多于上述收入水平的收入,他将被关进监狱。 [14]
这些法令的实际效果平平。仅在两年后,另一项法令——1351年的《劳工条例》提道:
据说雇工们,不顾条例,而是遵从自己所愿和过分的贪婪,不愿为上流人士或其他人工作,除非他们得到两倍或三倍于上述所说的他们早已习惯接受的本王统治第二十年以及更早前工资的工资。这对上流人士伤害极大,也使下议院议员变得贫穷。
这一法案还试图通过更加详细的限制和惩罚来弥补之前的失败。然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些措施又失败了。在14世纪90年代初,莱斯特的奥古斯丁教会的亨利·奈顿教士在他的编年记录中写道:
工人是如此的自高自大和残忍,以至他们根本不在意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用他们,就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因为雇主没有选择:如果不迎合工人的傲慢与贪婪,他的水果就无法采摘,成熟的粮食就无法收割。 [15]
用不带偏见的方式重复这位教士的表述就是,在市场力量面前,试图通过政府法令和强压维持工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在工人的联合阵线面前,雇主特别是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利益,超越了他们无法实现的集体利益。英格兰如此,其他地区亦如此。在1349年,法国人同样试图将工资控制在瘟疫前的水平,但以更快的速度宣告失败:在1351年,一项被修正的法律已经允许工资提高1/3。不久之后,雇主但凡需要雇人,都必须支付时下的工资。 [16]
多亏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很多关于熟练和非熟练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有时,一些数据还能追溯到中世纪,并且这些数据都是标准化的,有助于我们进行跨时期和跨地区的系统比较。11个欧洲和地中海东部城市的非熟练工人工资的长期趋势是很清晰的。我们只有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及伊斯坦布尔这很少几个地方的瘟疫前工资水平的信息——它们在瘟疫暴发前很低,之后就快速上涨了,实际收入在15世纪早期或中叶达到顶峰,当时其他城市也有相应的数据,并且显示了类似的水平。从大约1500年起,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实际工资都趋于下降,到1600年左右恢复到瘟疫前的水平,并在此后的200年间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下降到更低水平。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则是例外。它们的工资水平在整个前现代时期都保持了相当不错的水平,尽管后两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在15世纪后期出现了短暂的大幅下降,但后来又恢复了。与瘟疫相关的工资上升以及其后的下降在图中都表现得相当明显——幅度分别为100%和50%(见图10.1)。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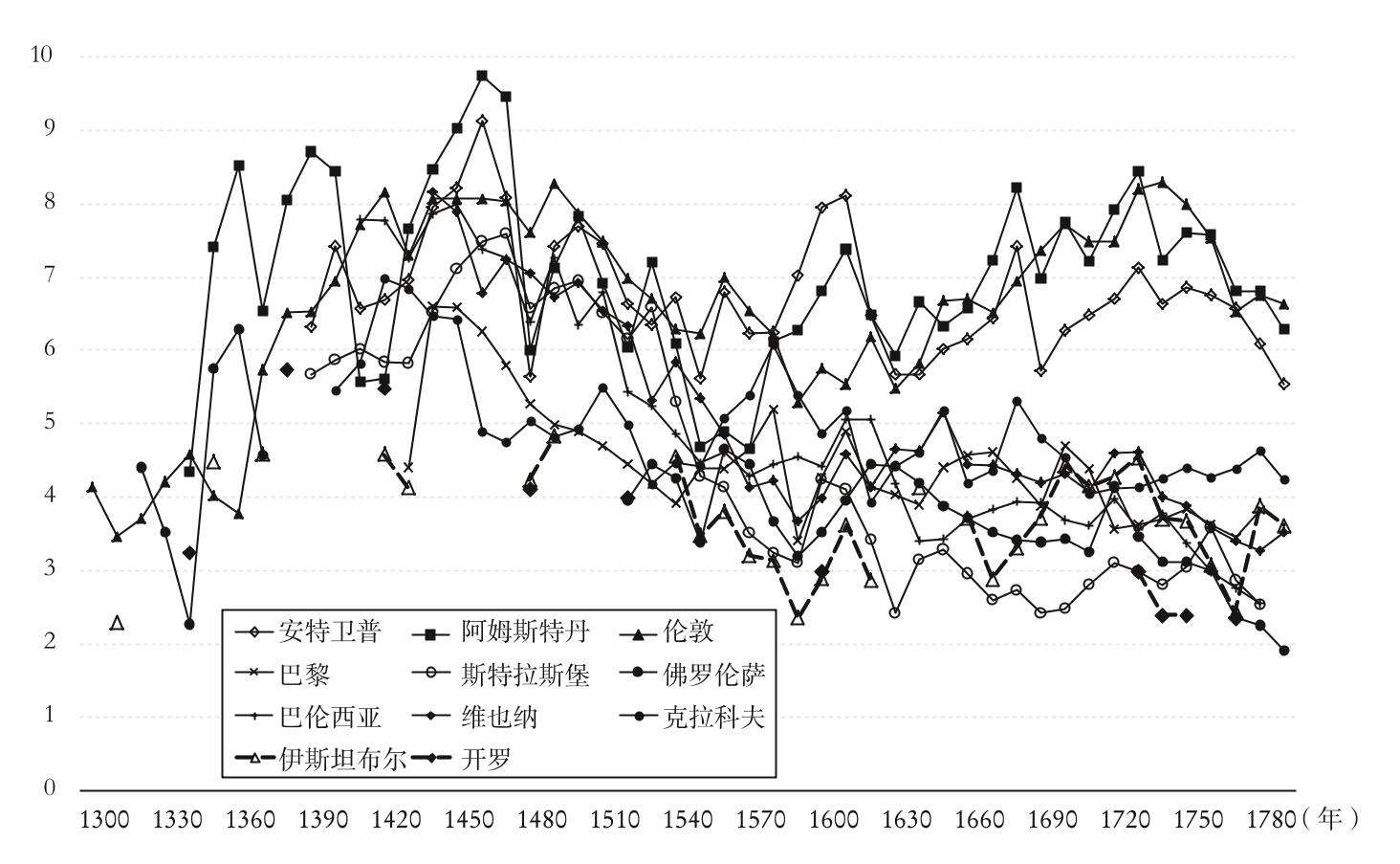
图10.1 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城市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1300—1800年
14个城市的熟练工人工资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地方数据显示,其工资从瘟疫开始时期到15世纪中叶大约翻了一番,而在1500—1600年逐-渐下降,此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继续下降直到1800年。之前的三个西欧、北欧国家再次成为例外(见图10.2)。 [18]
人口变化与实际收入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在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工资在人口数量降到最低点后不久达到了顶峰。人口恢复扭转了工资增长的趋势。在很多地方,1600年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实际工资持续下降。虽然对农村工资的记录较少,但英国资料显示,瘟疫确实带来了工资的大幅增长(见图10.3)。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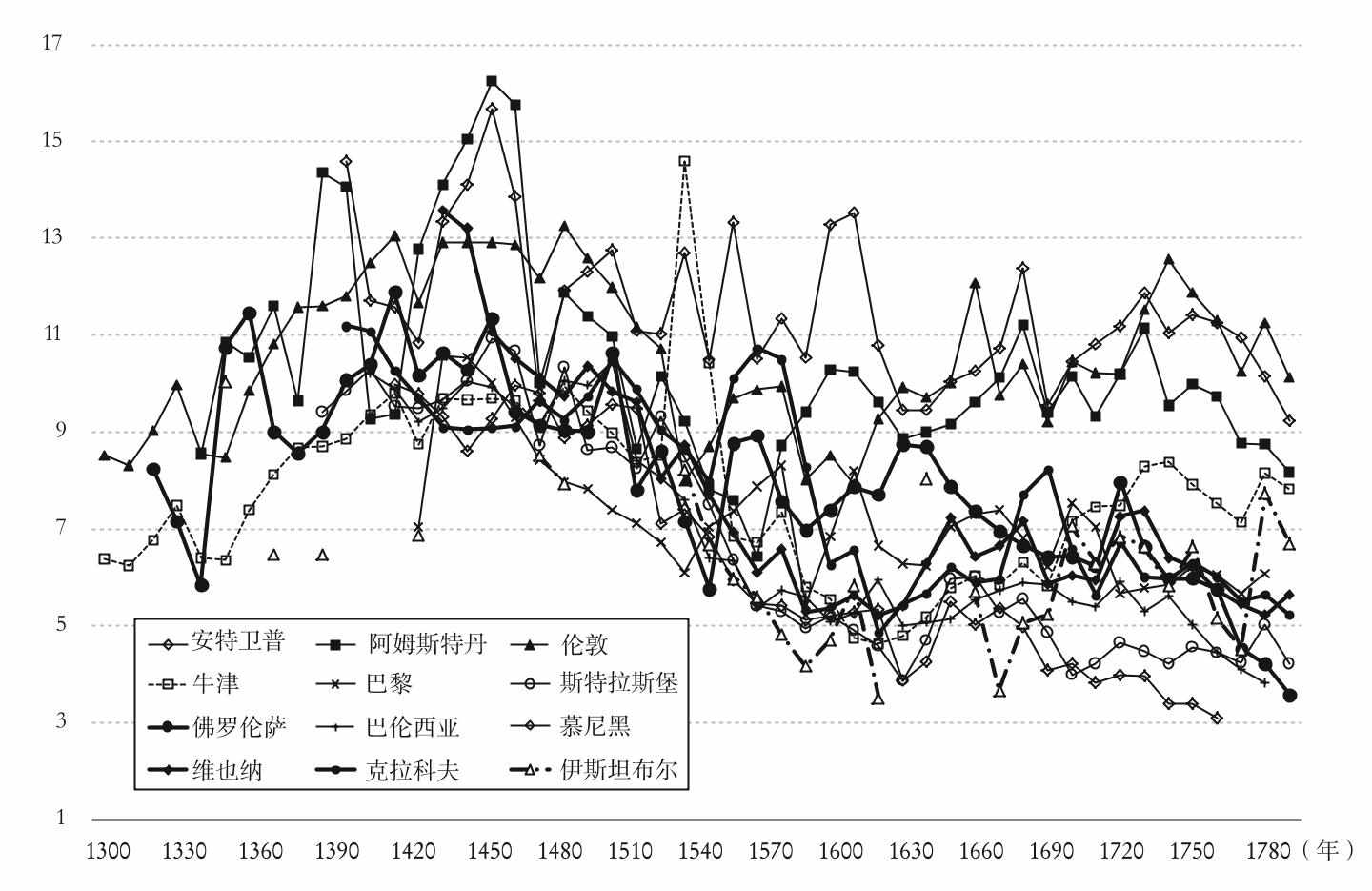
图10.2 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城市熟练工人实际工资,1300—18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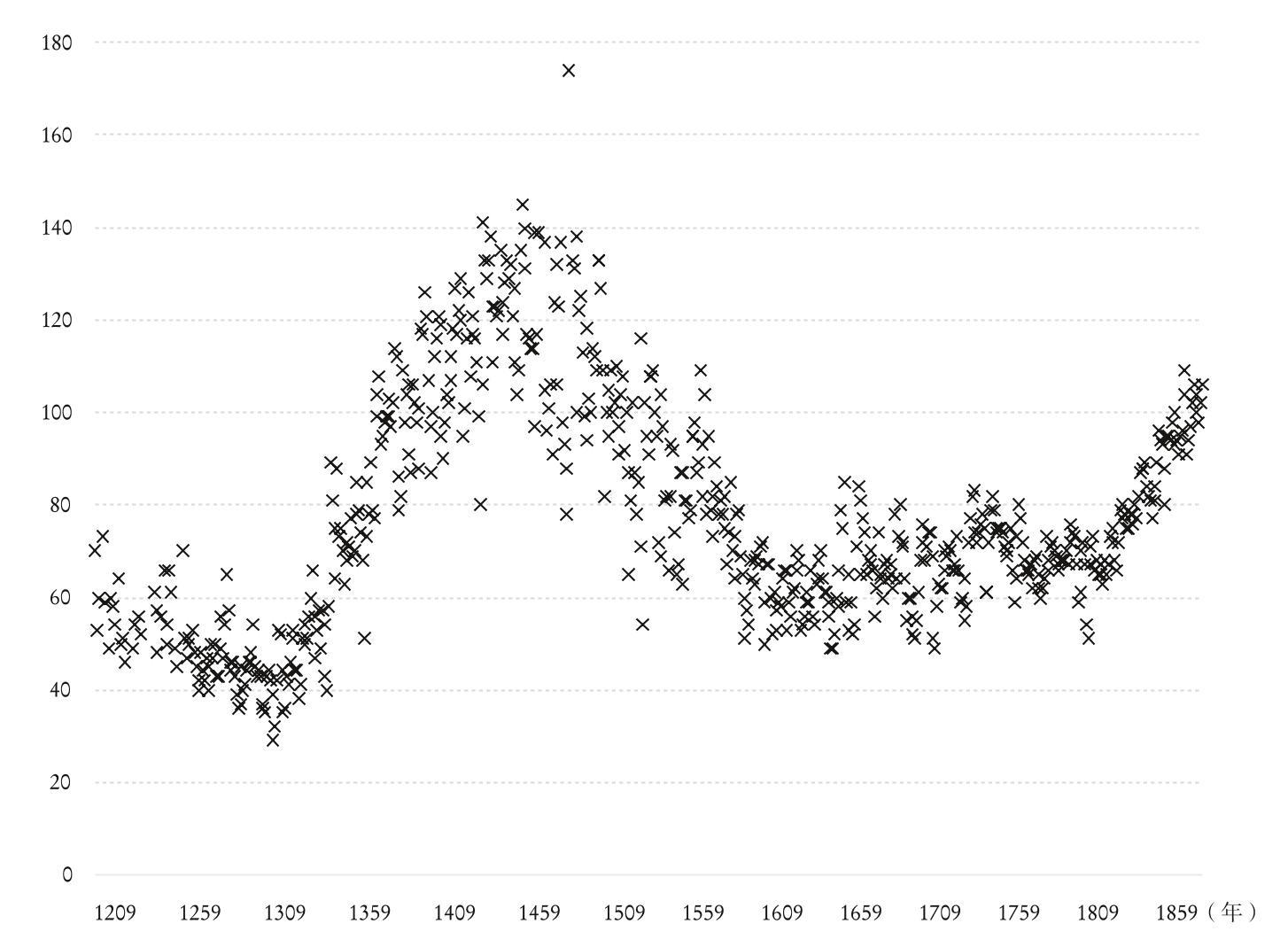
图10.3 用谷物衡量的英格兰地区农村实际工资,1200—1869年
在地中海东部也可以看到类似结果。黑死病肆虐之后,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尽管持续时间短于欧洲。正如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所说:
工匠、雇工、搬运工、仆人、马夫、织工、帮工等诸如此类——他们的工资增长了许多次;然而,能够享受这种增长的人不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只有耗费大量时间,才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工人。
来自瘟疫受害者的遗赠和继承财富的幸存者的馈赠推动了宗教、教育和慈善捐助激增。这些捐助鼓励了许多建筑工程的出现。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工匠同城市非熟练工人一同受益了。生活水平一时的提高增加了肉类需求:根据收入和价格的精细分解,14世纪早期,一个普通开罗人每天可能消耗1154卡路里,具体包括45.6克蛋白质和20克脂肪,但到15世纪中叶,他们可以消耗1930卡路里,包括82克蛋白质和45克脂肪。 [20]
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上展现出一幅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体相同的图景。到1400年,拜占庭城市的实际工资已经高于瘟疫前的水平,这与奴隶价格翻了一番的情况是一致的。奥斯曼帝国的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工人的实际收入直到16世纪中叶仍然很高,直到19世纪末,这个收入水平从来没有被系统地超越过,这凸显了瘟疫对工资上升产生了多么突出的影响。 [21]
尽管黑死病产生的影响很严重,但一次黑死病的肆虐不足以使城市实际工资翻一番,并在之后维持这一水平达数代人之久。反复遭受瘟疫才会阻止人口迅速恢复。中世纪晚期的记录证明,瘟疫是不断发生的。瘟疫在1361年重现,从那年春天持续到来年春天。由于它夺走了大量年纪不大的人的生命,被称为“儿童瘟疫”。总之,这次瘟疫似乎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瘟疫第一次暴发时还没有出生的人。它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仅次于黑死病本身造成的死亡:现代人猜测,欧洲人口在这次瘟疫中损失了10%~20%,英国损失了1/5人口。第三次毁灭性相对较小的瘟疫暴发于1369年。这为下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的一段时期定下了基调。仅英国暴发全国性传染病的年份就有:1375年、1390年、1399—1400年、1405—1406年、1411—1412年、1420年、1423年、1428—1429年、1433—1435年、1438—1439年、1463—1465年、1467年、1471年和1479—1480年。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数量特别大的人口死亡,并在1479—1480年的传染病流行中达到顶峰,这是自1361年以来的最糟糕的事件。系统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样糟糕:我们知道荷兰1360—1494年间发生了15次传染病,西班牙在1391—1457年间发生了14次。在欧洲,每一代都会遭受两三次的瘟疫袭击,把人口数量压制在低位。结果,到15世纪30年代,欧洲的人口可能已经是13世纪末左右的一半或更少。因地而异,人口恢复最终开始于15世纪50年代,15世纪80年代或16世纪末。我们所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几代人的不幸和数千万人的早夭为代价的。 [22]
关于瘟疫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知道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很清楚。与富人相比,土地和粮食价格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势必更有利于穷人,从而有可能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依靠反映这些变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对小麦的需求下降,但肉类、奶酪和大麦(大麦用于酿造啤酒)的价格持续上涨,这表示劳动者的饮食改善了,他们获得了以前那些曾经是富人专利品的食物。奢侈品需求增长更为普遍。除了更高的工资外,英国工人还可以要求让肉馅饼和麦芽酒作为他们的一部分补偿。对诺福克的农民来说,面包在饮食中的份额从13世纪末的接近一半下降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15%~20%,同期肉类的份额从4%上升到25%~30%。
英国的两项禁奢法令构成了显示这种大矫正存在的强烈信号。1337年,议院发布法令,只有年度收入为1000磅以上的贵族和牧师才有资格穿象征身份地位的皮草。但是,在黑死病暴发后的15年内,1363年的一部新法允许收入最低的手工劳动者外的所有人穿皮草。当局只是试图规定哪些人能穿哪类皮草,从规定社会底层能穿兔子皮和猫皮制品,到规定社会上层能穿白裘皮草。即使是这些相对温和的限制也变得形同虚设,这显示社会大众普遍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界限被不断打破。 [23]
当普通人现在能够负担起过去曾经是精英独享的物品时,贵族却因他们土地上农产品的价值下降和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工人的工资上涨而危机四伏。在佃农染病死亡后,地主不得不另外雇用劳动者甚至雇用更多劳动者进行农耕以获得好的收成。那些仍然被雇用的佃农享受到了更长期的租约和更低的租金。社会的变化逆转了早前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富裕而大多数人相对贫苦的趋势,社会变成另一番场景:在长达约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里,精英获得的社会剩余变少,而其他人获得更多。在英国,土地出租人的收入单单在15世纪上半叶就下降了20%~30%。乡绅饱受地位下降之苦,大贵族也不得不设法在收入减少时保持他们的身份。瘟疫导致了贵族阶级的急剧萎缩:仅两代人的时间,在新贵族出现的情况下,总量占3/4的贵族家庭因后继无人而湮灭了。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财富都收缩了:按照可比的实际收入门槛,13世纪绶带骑士数量翻了三番,达到3000名左右,但1400年时人数已经降到2400名,1500年时降到1300名。最上层贵族人数从1300年的200人下降到1500年的60人,这通常是由有些家族阶级地位下降和一些家族在财富下降后合并造成的。贵族的最高收入纪录在14—15世纪之间也大幅下降。 [24]
这些整体发展趋势是显示社会矫正度的重要指标。只是最近几年才终于有坚实的量化证据出现来支持这一点。在一个原创性的研究中,圭多·阿尔法尼搜集并分析了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档案馆的数据。当地财产登记册中保留了该市资产分布的信息。其中许多人只记录了地产情况,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如著名的1427年佛罗伦萨的卡塔斯托登记册的详尽记录那样记录包括其他类型的资产,如资本、信贷和动产的分布。这些局限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成为我们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唯一可用变量。阿尔法尼的调查基于来自13个皮埃蒙特社区的数据。虽然最久远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366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15世纪晚期以后的数据。通过后一时段,我们观察到了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城镇18世纪的基尼系数都高于中世纪。城市和农村都如此——不管是通过基尼系数还是用最富的前5%群体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来衡量不平等程度,两者均呈现于图10.4。财产集中的总体趋势对应着现代社会早期的经济扩张引起的所谓“超级曲线”的上升阶段,这部分我在第3章讨论过了。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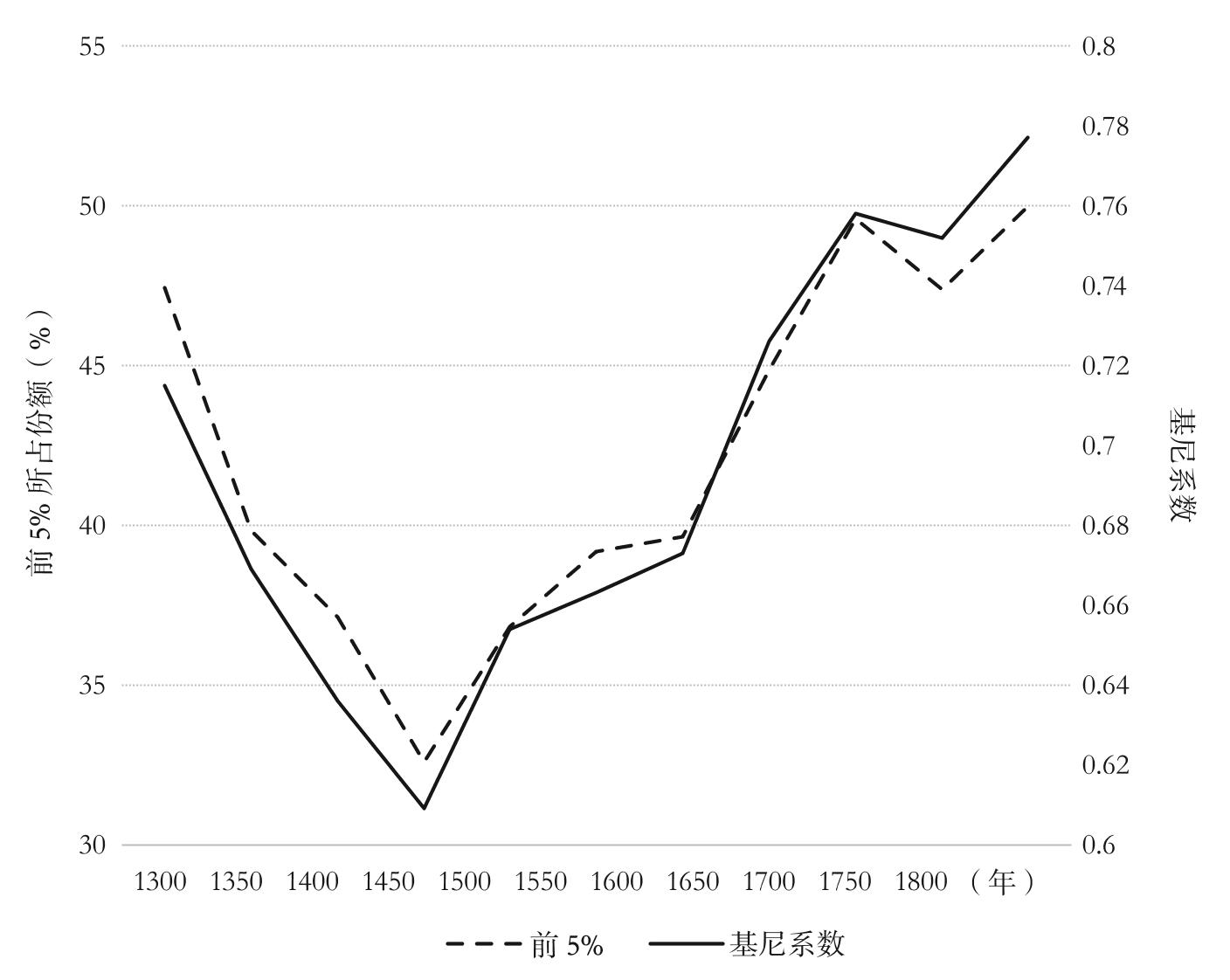
图10.4 皮埃蒙特地区顶层5%群体的财富份额及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00—1800(参考年份经过平滑处理)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出现在瘟疫之前和瘟疫发生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三个城镇,奇里、凯拉斯科和蒙卡列里的数据是可以获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图10.4中1450年前的城市数据),14世纪和15世纪初,不平等程度下降,这一时期瘟疫周而复始。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的一些社区,拥有至少10倍于当地家庭财富中值的家庭的数量比例在同一时期减少了。这一矫正效果与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实际工资数据相当吻合:在佛罗伦萨附近,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同一时期大约翻了一番(见图10.1)。在与瘟疫相关的冲击导致精英内部变动时,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使工人更容易获得财产。财富分配曲线的形状同样变化明显,不平等程度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时刻与人口数量降至最低后逐渐恢复的人口统计的转折点也是吻合的。 [26]
与大多数实际工资序列的情况相同,这种不平等程度的缩小情况并不会持续。15世纪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度不仅上升,而且在那之后一般都在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1630年瘟疫再次暴发,这是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地区性死亡危机,它被认为杀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1/3以上的人口,但对不平等的影响不似从前:公元1650年或1700年的基尼系数和最高财富份额始终一致地高于它们在公元1600年时的数值,即使公元1600年已经过之前150年的恢复。这表明,黑死病暴发以及随后的再次暴发打击了不善于应付其后果的地主阶级,而在它们之后,有产阶级最终发展出了在人口冲击时期保护其财产的应对策略:诸如将财产部分赠予第三者的遗嘱(允许一个家族在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时也可保留财产)那样的制度可能有助于保持精英财富完好无损。看来,即使是最可怕的传染病也可能被文化学习驯服,从而削弱了马尔萨斯抑制的矫正效应。 [27]
根据托斯卡纳各地的财产税的档案数据,我们可以画出非常相似的图形。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是,波吉邦西农村地区1338—1779年的财富分布被完整地记录在案,并表现出了在黑死病肆虐时期的矫正作用以及其后不断的财富集中(见图10.5)。佛罗伦萨境内其他十个乡村社区以及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的城市的可比数据虽并未全都显示出类似清晰的结果,但其整体趋势趋同(见图10.6)。唯一观察到的显著下降时期是瘟疫横行时期;在农村地区,不平等大致从1450年左右开始增长;从1600年左右开始,可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几乎总是高于之前的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达到顶峰。另外,在一些社区,洛伦兹曲线在黑死病暴发后一下子就变得平坦了,这表明矫正主要受富人的损失驱动。 [28]

图10.5 波吉邦西地区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38—17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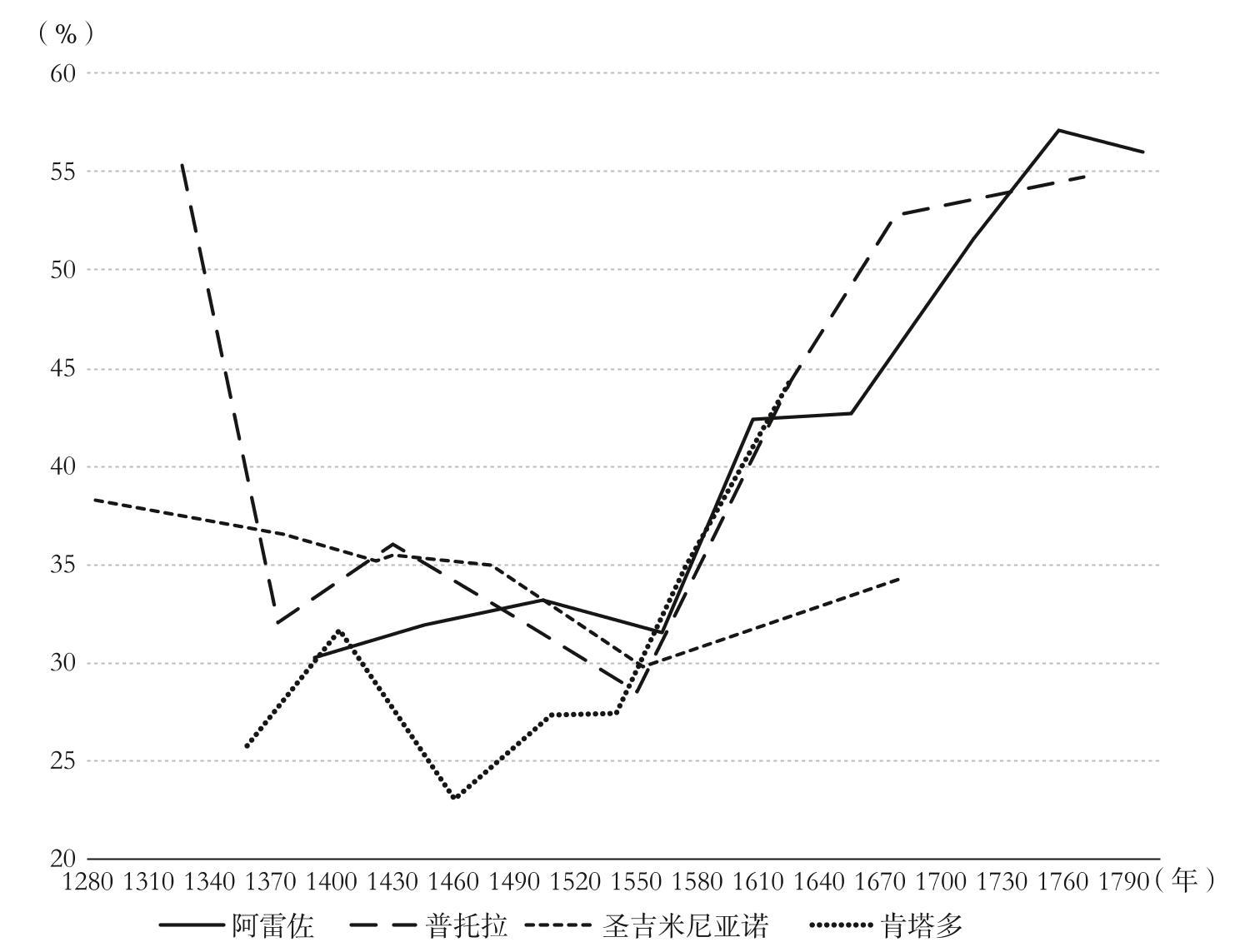
图10.6 托斯卡纳地区顶层5%群体所占财富份额,1283—1792年
这些动态变化机制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卢卡境内,这里的不平等程度在瘟疫肆虐时急剧下降,瘟疫过后又迅速回复(见图10.7)。现在,也有证据表明,1500年左右至1600年,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的财富出现了集中,但它们没有瘟疫前的资料可供我们做对比。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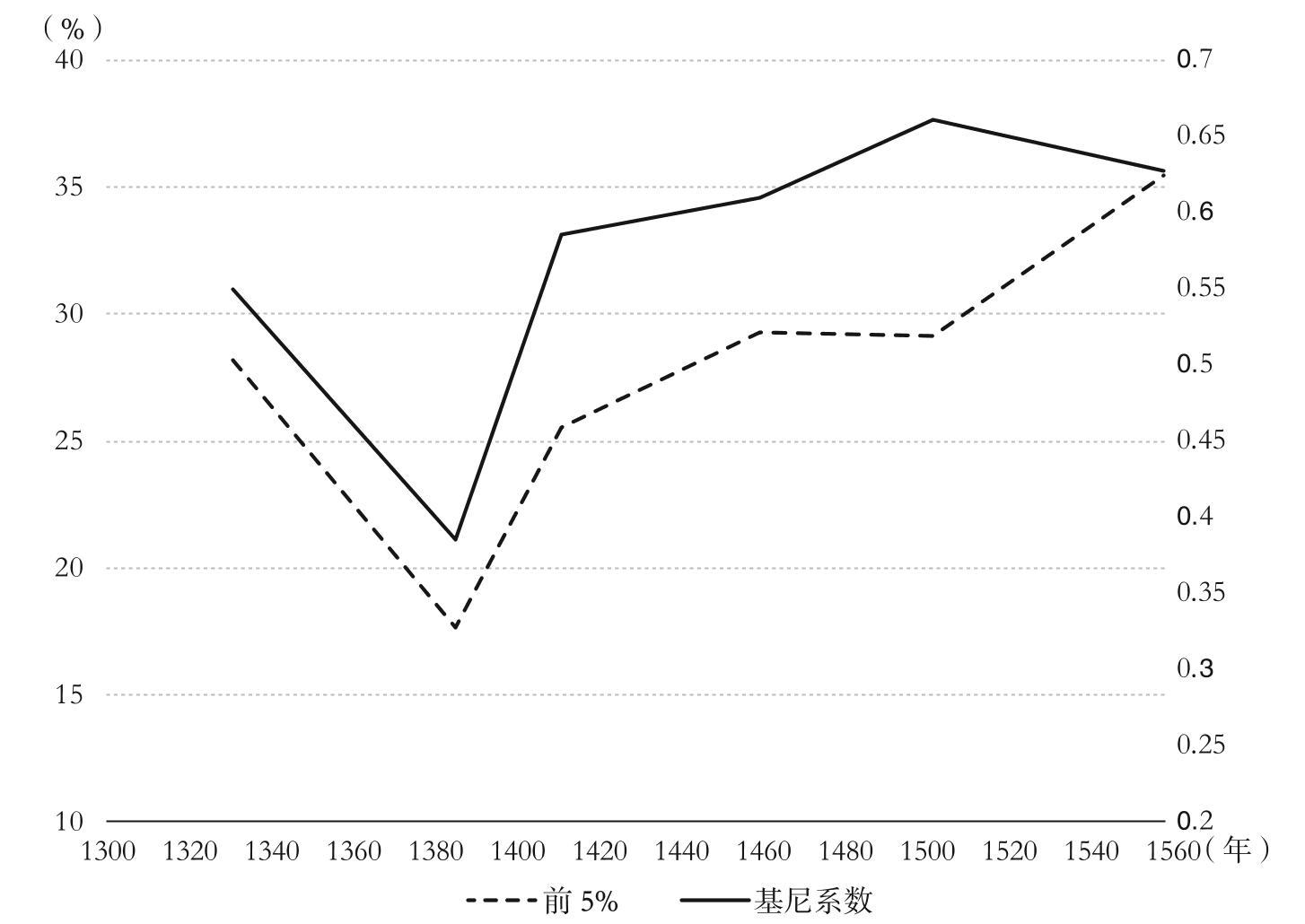
图10.7 卢卡地区顶层5%群体所占财富份额和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31—1561年
17世纪的意大利的经验凸显了人口变化以外因素的重要意义。将工资稳定在瘟疫前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这一点前面已经做过说明。精英有强烈的动机来遏制黑死病及其复发的矫正作用。他们采取的措施成功与否因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甚至社会环境而天差地别。在西欧,工人受益匪浅,因为由劳动力匮乏所产生的好处落到了他们身上。不仅对工资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未能产生作用,而且瘟疫对人口的冲击摧毁了早前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农民维护自身流动性,如果其他庄园主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便投靠新主。这压低了租金,减少并最终消灭了作为庄园经济标准特征的劳工无偿服役制度。佃户最终只支付租金,并有机会尽可能多地耕作土地,只要自己的能力允许。这促成了农民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并使富农发展为自耕农阶级。英格兰的雷德格雷夫庄园就是一个例子,1300年农民平均耕作12英亩土地,1400年为20英亩,到1450年,已经超过30英亩。整个西欧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到1500年,在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所谓的根据官册享有不动产成为主导性的租期安排:合同规定了固定的年租金,它根据佃农通过议价获得的最佳结果确定。 [30]
有时工人采取暴力来抵制精英,试图否认精英新获得的成果的企图。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其结果就是普遍的农民起义,如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和英格兰1381年的农民起义。后者的导火索是开征人头税,这种税表面上用来弥补国家收益的减少,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那些想要维持其经济特权地位的地主的愿望的:起义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得到自由谈判雇佣劳动合同的权利。从短期来看,这次起义被强力镇压了,但新的限制性法规得到通过,理查德二世也向农民说了一通著名的狠话:“你们会遭受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奴役。”但是,这一法规确实向农民让步了:人头税被取缔,农民的议价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时期的守旧诗人叹息道,“这帮匹夫”,他们“窥视到世界需要服务和人工……仗着劳动力稀缺,傲慢无礼”,“看,他们什么都没干就狮子大开口”。大体上可以说,工人受益于劳动力稀缺,至少在它持续的时候是这样。 [31]
然而在其他地区,地主更成功地镇压了工人的议价行为。在东欧国家——波兰、普鲁士和匈牙利,农奴制在黑死病暴发后被引入了。杰尔姆·布卢姆给这个过程做出了一个经典叙述。他在1957年观察到,中欧和东欧那时面临着西欧经历过的人口减少、土地没有主人、土地和粮食价格下降问题。拥有土地的贵族采取法律措施,以阻止收入下降,规定工资和城市物价上限。与西欧不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劳动义务,特别是劳动税捐、现金缴纳和对劳工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诸如普鲁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利沃尼亚等不同国家,佃农完全被禁止在未经许可或不支付大笔费用或全部欠款的情况下离开,除非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情况下。挖走他人雇工的行为是被法律或贵族协议禁止的。按照命令,城市可以拒绝移民,统治者就将移民遣回原籍达成协议。债务是贵族限制佃农的强大工具。负担和限制在16世纪继续增加。许多因素共同制约着工人的发展,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贵族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的管辖权越来越大,同时商业化和城市化方面也出现了不利于工人的发展。由于贵族以牺牲国家为代价扩大其权力,而城市没有能够出现抗衡这一趋势的力量,工人陷入越来越多的强制性安排之中。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改良者花费大量时间质疑这种阶级重建,但是东欧工人的状况与西欧工人状况相去甚远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32]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则发展了一套不同的限制手段。如前所述,这个国家被黑死病重创,城市的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和其他地区一样确实上升了——至少起初是这样的。然而,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配置使精英能够拒绝工人的要求。作为外来的征服者,马穆鲁克用一种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的方式控制了土地和其他资源。马穆鲁克的统治阶级成员从个人伊克塔(一种伊斯兰土地税收制度)取得收入,它是土地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分配机制。每当利润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农业出现问题而下降,国家的默认应对措施是通过更多地压榨数量减少的纳税人来提升统治阶级的权益。在城市中,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也意味着充公、强买强卖和垄断的形成。这些强制性应对措施解释了中世纪晚期的开罗资料中工资只在短期内有所增加的记载。 [33]
对农村地区的压制有过之无不及。马穆鲁克人是脱离土地的不在位食利者,他们无法、也不愿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土地所有者随时准备在环境变化后与农民进行谈判。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负有维持租金流的责任,它将马穆鲁克人同土地耕作者分开了。这些管理者随时准备对农民施加压力,在方便时还能诉诸武力。农民通过转移至城市甚至起义来反抗。贝都因人占据了废弃的土地,这一过程进一步减少了基础收入。此外,由于埃及环境的特殊性,瘟疫和逃亡造成的人力损失势必破坏严重依赖日常维护的精良灌溉系统,这使得埃及的农业资产比欧洲的农业资产更加脆弱。因此,如果可耕地数量迅速下降,埃及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的变化可能不如欧洲的比例变化那么大。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依靠集体主义进行剥削和控制了国家的马穆鲁克在集体谈判权力上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中间管理层造成的统治阶层脱离土地、有关使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的技术升级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资源基础的恶化——压低了农村地区的产出与收入。这与带来了更高的工人收入和显著矫正效应的西欧契约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34]
黑死病带来的后果以及17世纪意大利瘟疫再次暴发期间持续的不平等现象说明,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本身也无法使财富或收入分配变得平等。制度设置可以弱化人口冲击的影响,统治者通过强制性措施来控制劳动力市场。一种形式的暴力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抵消:如果细菌传播被足够强大的人类力量压制,精英可以维持或者快速恢复巨大的不平等。这意味着瘟疫的矫正效应存在两方面的限制:时间方面,随着人口恢复,平等化的成果都不可避免地趋于消亡;矫正效应的有无和大小受制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只有在某些情况、某些时期,传染病才可以大大减少不平等。
[1] Quoted from Malthus 1992: 23 (book I, chapter II) using the 1803 edition.
[2] Responses: the work of Ester Boserup is a classic (Boserup 1965; 1981).See esp.Boserup 1965: 65–69; Grigg 1980: 144; Wood 1998: 108, 111.Models: Wood 1998, esp.113 fig.9,with Lee 1986a: 101 fig.1.Malthusian constraints: e.g., Grigg 1980: 49–144; Clark 2007a:19–111; Crafts and Mills 2009.Inputs: see Lee 1986b, esp.100 for the exogeneity of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seventeenth-century resurgence in England.
[3] I mainly follow Gottfried 1983, still the most systematic study, and Dols 1977 for the basic narrative and Horrox 1994 and Byrne 2006 for primary sources.
[4] Gottfried 1983: 36–37.
[5] Byrne 2006: 79.
[6] Gottfried 1983: 33–76.
[7] Gottfried 1983: 45.
[8] Horrox 1994: 33.Mass graves: the Black Death Network, http://bldeathnet.hypotheses.org.Cf.also herein, chapter 11, p.231.
[9] Horrox 1994: 33.
[10] Gottfried 1983: 77; cf.also 53 (35–40 perc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unpublished work cited by Pamuk 2007: 294; Dols 1977: 193–223.
[11] Quoted by Dols 1977: 67.Gottfried 1983: 77–128 discusses the plague’s manifold consequences.
[12] E.g., Gottfried 1983: 16–32; Pamuk 2007: 293.See herein, pp.331–332, for the crises of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13] Horrox 1994: 57, 70.
[14] Horrox 1994: 287–289.
[15] Horrox 1994: 313, 79.
[16] Gottfried 1983: 95.
[17] See esp.Allen 2001; Pamuk 2007; Allen et al.2011.Fig.10.1 from Pamuk 2007: 297 fig.2.
[18] Fig.10.2 from Pamuk 2007: 297 fig.3.
[19] Population and income: Pamuk 2007: 298–299.Fig.10.3 compiled from Clark 2007b: 130–134 table A2; see also 104 fig.2.
[20] Rapid rise: Dols 1977: 268–269, and cf.255–280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lague in general.Europe: Pamuk 2007: 299–300, and see herein, Fig.5.9.Quote from Dols 1977: 270.Endowments: 269–270.Diet: Gottfried 1983: 138, derived from work by Eliyahu Ashtor.
[21] Byzantium: Morrison and Cheynet 2002: 866–867 (wages), 847–850 (slaves).Istanbul:Özmucur and Pamuk 2002: 306.
[22] Gottfried 1983: 129–134 gives a succinct summary.
[23] Pamuk 2007: 294–295 (luxury goods); Dyer 1998 (changes in living standards); Gottfried 1983: 94 (ale and pies);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40 (Norfolk); Gottfried 1983: 95–96(laws).
[24] Gottfried 1983: 94, 97, 103.Tenant contracts: Britnell 2004: 437–444.Land incomes: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65.Heirs: Gottfried 1983: 96.Elite numbers and fortunes: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56, 71–72, 78.
[25] Alfani 2015.Fig.10.4 from 1084 fig.7, using the data at http://didattica.unibocconi.it/mypage/dwload.php?nomefile= Database_Alfani_Piedmont20160113114128.xlsx.For breakdowns by cities and villages, see 1071 figs.2a–b and 1072 fig.3.
[26] Decline in share of wealthy households: Alfani 2016: 14 fig.2 [recte fig.3].For this measure, see herein, chapter 3, 92.
[27] See esp.Alfani 2015: 1078, 1080, and see also Alfani 2010 for a case study of the plague effects in the city of Ivrea in Piedmont, where postplague immigration of the poor immediately raised urban wealth inequality.Figs.10.1–2 show that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lague did not have a consistent effect on urban real wages.Thes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ate medieval and seventeenth-century plague phases underline the need for more systematic comparative study.
[28] Alfani and Ammannati 2014: 11–25, esp.19 graphs 2a–b, 25 fig.2.They also demonstrate why David Herlihy’s earlier claims of rising Tuscan inequali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are incorrect (21–23).Figs.10.5–6 are from 15 table 2 and 29 table 4.
[29] Fig.10.7 from Ammannati 2015: 19 table 2 (Ginis), 22 table 3 (top quintiles).Lombardy and Veneto: Alfani and di Tullio 2015.
[30] Gottfried 1983: 136–139.
[31] Gottfried 1983: 97–103; Bower 2001: 44.See also Hilton and Aston, eds.1984, also for France and Florence.
[32] Blum 1957: 819–835.Revisionism has now culminated in Cerman 2012.
[33] Dols 1977: 275–276.See herein, Fig.11.2.However, Borsch’s argument that certain urban real wages had fallen precipitously between 1300/1350 and 1440/1490 seems hard to sustain: see Borsch 2005: 91–112, with Scheidel 2012: 285 n.94 and, more generally, Pamuk and Shatzmiller 2014.
[34] Dols 1977: 232; see 154–169 for rural depopulation, and see 276–277 for revolts in the late fourteenth century.Combination: Borsch 2005: 25–34, 40–54.Contrast: Dols 1977: 271, 283.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 [1]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阿兹特克观察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的脸上、乳房和肚子上都长满了疮,我们从头到脚都感到痛苦。这种病太可怕了,没有人可以走路或移动。病人非常无助,只能像尸体一样躺在床上,无法移动四肢甚至头部,不能趴着躺,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们稍微移动身体,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 [2]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 [3]
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多级统治被类似的西班牙多级统治取代,财富的演变必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变化的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才能确定人口变化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胆尝试勾勒出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没有细节的历史”,他观察到标准的马尔萨斯逻辑所预测的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实际工资上升发生在16世纪,但他无法引证支持这种猜想的证据。2014年,一项有关拉丁美洲的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随后三个世纪的收入的开创性研究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图11.1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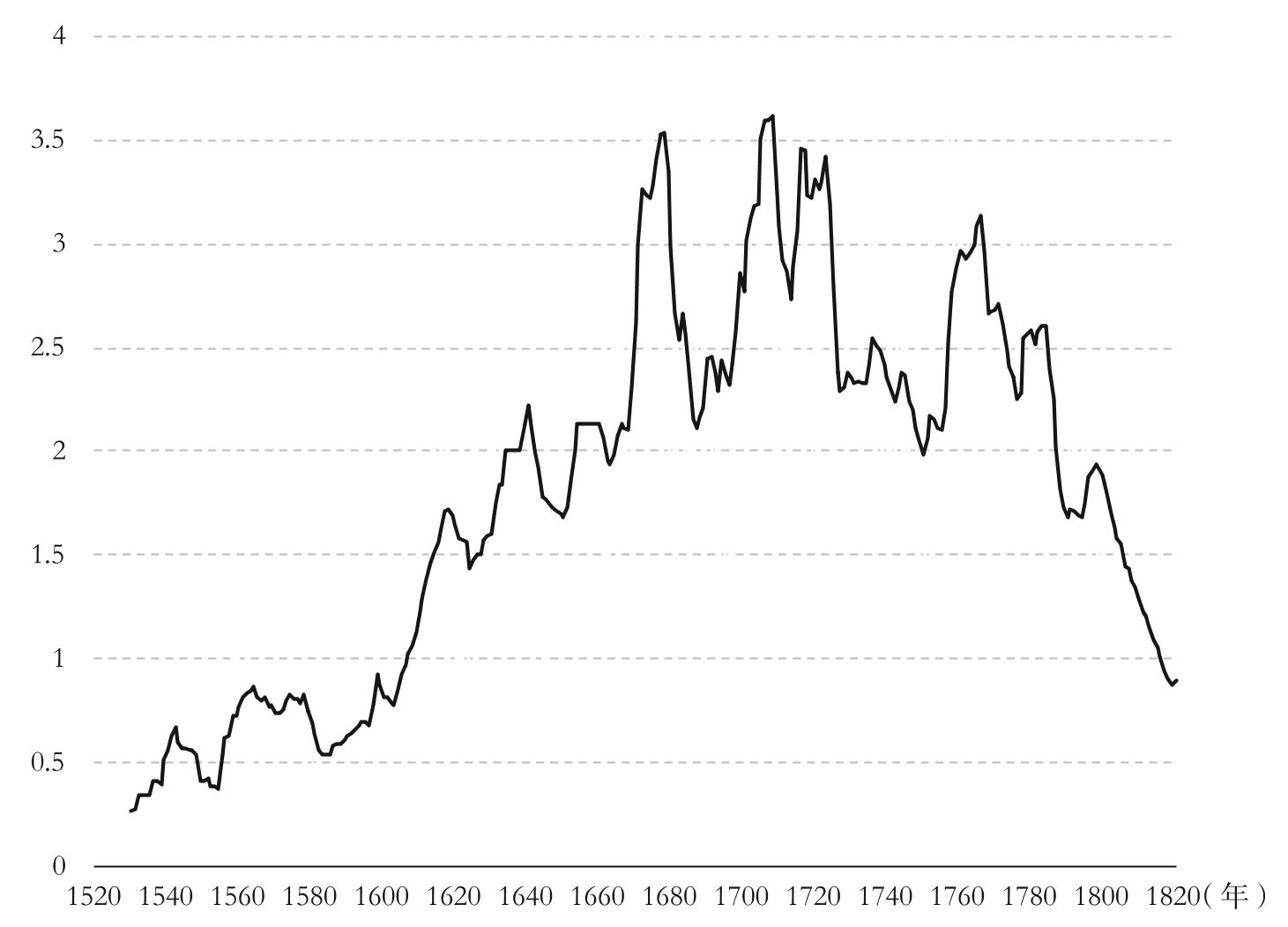
图11.1 在墨西哥中部,实际工资用大量的消费篮子表示,1520—1820年(10年移动平均值)
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但是,在16世纪的瘟疫死亡率特别高的时期,工资没有上涨,这确实需要解释。答案可能在于西班牙人依赖强制劳动确保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得到劳动力保障,这种做法根植于前哥伦布时期的强制劳动制度。因此,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抑制工资谈判。这种解释与西班牙在墨西哥统治初期所实施的高压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大授地制”(一种允许美洲征服者从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劳动和贡品并据为己有的制度)是征服美洲的第一代精英获得薪酬的标准形式。这种制度在1601年被废除(采矿业除外),而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7世纪30年代。但此前,适用这种制度的领地总数量已经从1550年的537个下降到1560年的126个。
起初工资所受到的严格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放松。16世纪的墨西哥,总督决定工资,高压政策无处不在。从17世纪早期开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实际工资得以提高。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1590年,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但到1700年,其实际工资水平并不比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低多少。如果观察到的16世纪的工资水平滞后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随后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就使劳动力的稀缺性反映在实际的劳动报酬水平上。与西方黑死病影响不大时的欧洲劳工法不同,在墨西哥,根深蒂固的强制劳动模式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干预权力。工人获得额外好处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到1810年,工人工资又回到了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5]
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实际工资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巨大的规模,工资水平增长了4倍,而黑死病后的西欧城市的工资水平仅仅增加一倍。这与墨西哥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可能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后来的实际收入下降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类似——尽管前者同样比后者下降得更多,且确实很难仅用人口恢复一个因素来解释。尽管这些变化的观测范围可能会使人们对记录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总体情况似乎是很清楚的。几代工人从劳动力短缺中受益,由于劳动力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市场机构无法阻止薪酬水平的调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又回到了原先的糟糕状态,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
一般情况下,生活标准和身高等福利指标与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然而,正如在前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确定这些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却对总体收入没有某种矫正效果,但现在,我们也只有这种基本的直觉。尽管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但公平地说,新大陆的数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与由瘟疫驱动的矫正逻辑以及几个世纪前欧洲发生瘟疫后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尽管西班牙的征服者会以为他们的位置是之前阿兹特克统治阶级的位置,从而保留了财富集中在社会顶端的格局,但哪怕仅仅是部分工人实际收入的大幅增加也会降低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即使它只是暂时的。17世纪的墨西哥很可能与15世纪的西欧一样,具有这一相同的特征。 [6]
为了进一步研究由流行病引起矫正效应的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 [7]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 [8]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已经确定,尽管受到了上帝——我们的主的惩罚,从事贸易和追求文学的人们,以及工匠、农民和水手,都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和薪金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古老的习俗。因此,看起来,我们通过这项帝国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这种可怕的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手艺人、商人、店主、农民都不得要求超过古代习俗规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资。我们还规定,从事建筑物、可耕种土地和其他财产测量的人不得超过合理收费标准,而应该遵循在这方面已确立的惯例。我们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购买原料的人遵守这些规定。我们不允许他们支付比日常惯例更多的金额。在此通知他们,任何要求超过这一规定收入标准的人,以及被认为已经接受或给予超过允许金额的人,将被强令支付三倍于那个数量的金额给国家财政。 [9]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见图11.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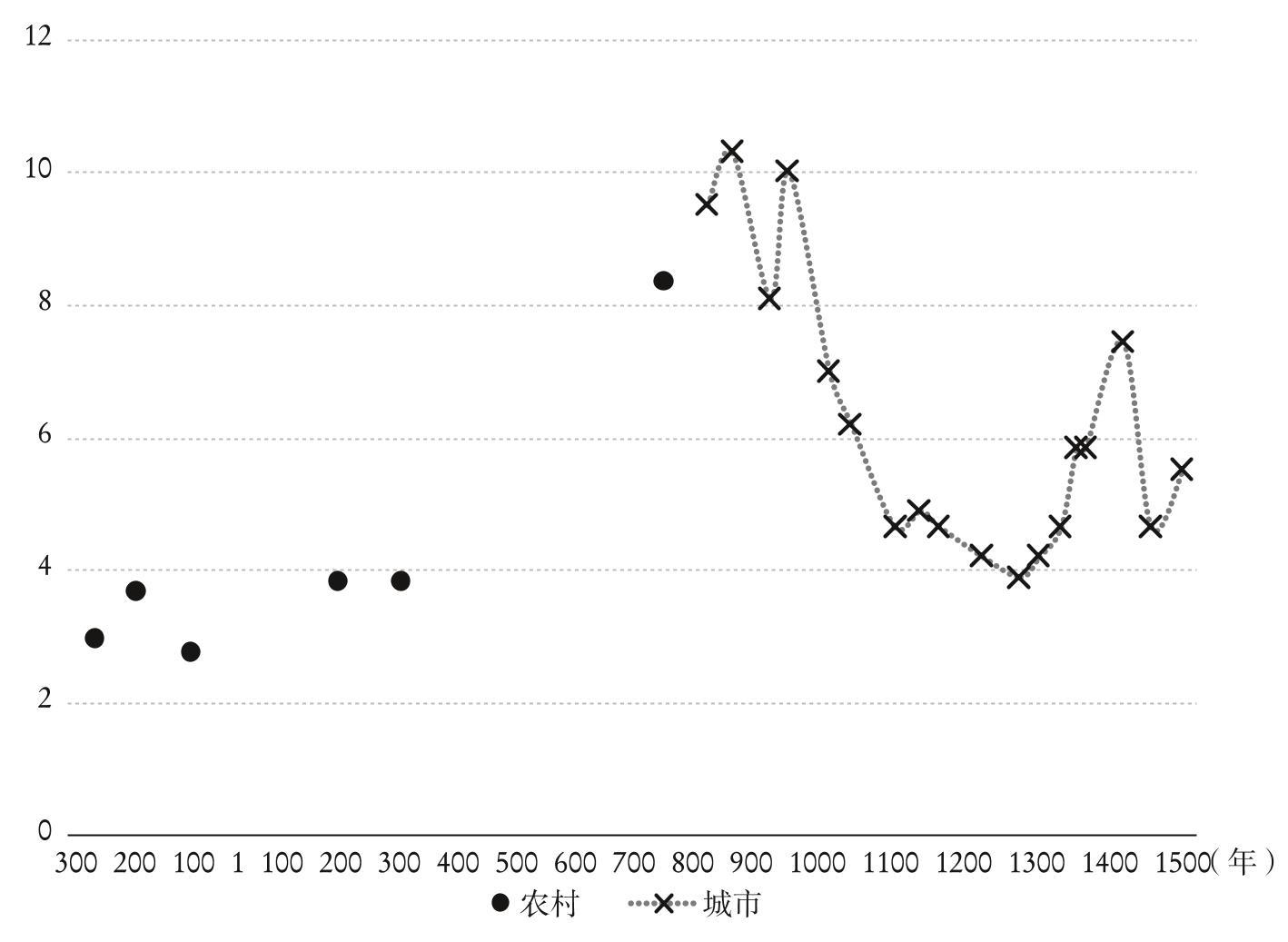
图11.2 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
查士丁尼瘟疫之后,这种没有技能的农村工人报酬的激增源自一种纸上记载的证据。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的几份记录中,当瘟疫对人口减少的影响达到顶峰时,灌溉工人每天的现金工资相当于13.1~13.4升的小麦,大约是以前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情形中,每天的现金工资和食品补贴总额超过了相当于7.7~10.9升的小麦,这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这些发现获得了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相当于25升小麦的水平。通过观察,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从6世纪的前半期到后半期,也就是第一次瘟疫暴发前后,签订永久租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17%上升到39%,而签订一年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29%下降到9%。这表明,佃农很快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条款。这一现象,尤其是实际收入的激增,只能放在大规模人口死亡,各行各业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议价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 [11]
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小麦工资。如图11.2所示,可获得的数据始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鼠疫末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实际工资一直在提高,持续到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在公元8世纪40年代埃及被最后证实存在鼠疫的一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实际工资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工资水平,即每天工资大约相当于10升小麦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基本生存所需的三倍水平。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随着人口的恢复,开罗的小麦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仅能维持最低生存需求的水平,直到14世纪末期黑死病出现才暂时恢复。来自巴格达的质量较低的数据也显示,在8—13世纪,实际收入也长期下降,尽管下降的规模较小。消费篮子的重建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消费篮子将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与一个基本范围内的消费品的价格联系起来。从这个重建也可以看出,鼠疫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接着是下降,然后是黑死病期间的另一次复苏:尽管变化的范围小于单纯的小麦工资变化的范围,但总体的模式是一样的。 [12]
如同中世纪晚期一样,查士丁尼瘟疫的反复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我们听说了10个在埃及的事件,覆盖从公元541—744年间断断续续的总持续时间为32年的瘟疫。也就是在这期间每6年多就发生1次瘟疫。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558—843年间,共经历了14次瘟疫,总持续时间为38年,也就是这期间每7.5年就有一次瘟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证实有更多疫情,但这些地区缺乏与收入相关的数据。谢夫凯特·帕慕克和玛雅·莎兹米勒追踪了公元8—11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由瘟疫带来的高薪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对欧洲一些地区的偏好和消费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工薪中产阶级中,人们普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这只有在畜牧业扩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化、与之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对制成品需求的增长,也包括极少数精英人士之外的人对进口食品和服装的需求。 [13]
然而,这些过程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我们的推测:在缺乏直接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真实工资的爆炸式增长确实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精英财富的减少。在这样一个无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而有记录的财产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环境中,理应出现一个更普遍的矫正手段。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瘟疫在一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来临。埃及的土地和税收清单对公元3—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记录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们忽略了跨地区的财富和没有土地的人,因此可能极大地低估了土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以,这些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实际财产集中程度的数据暗示着高度不平等:对于来自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样本,计算出的土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623~0.815;对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431~0.532。整个省或主要行政区重建土地所有权的结构表明,基尼系数为0.56只是对地主而言,而地主人数在理论上不超过总人口的1/3。我们假设,一个省只有一半居民是没有土地的工人或佃户(或者没有土地的人更少一些,但一些精英成员在其他省也拥有土地),土地的基尼系数将接近0.7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集中程度将与埃及1950年土地改革之前的高土地基尼系数类似,当时土地所有者的基尼系数是0.611,而全体人口的基尼系数是0.752。因此,在资产不平等问题上,由瘟疫驱动的矫正潜力相当大。 [14]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埃及的收入不平等是完全不可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即便如此,考虑到从土地到劳动的转变以及传统财富精英的损失,所有这些发展在逻辑上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经济分化和城市化将同时创造出新的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与马穆鲁克时期不同,集体旷工压制了工人的讨价还价,私有土地占支配地位,与相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起,创造了一个使资产估值和工资对土地与劳动力比率的变化非常敏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减少几乎不可能不削弱整体收入的不平等,就像土地价值的减少也倾向于减少财富不平等一样。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成了这次重建的最有力的因素,这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收入压缩的最好指标。这表明,国家试图遏制工资增长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就像他们在黑死病暴发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在人口复苏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逐渐被侵蚀。第一次“黑死病”的暴力冲击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福利,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这种冲击力也逐渐消失。在这方面,两次瘟疫大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
越是向更早的时期追溯,关于瘟疫的矫正效应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越加稀少。最好的一个案例是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征伐中第一次遇到了这种瘟疫,第二年瘟疫蔓延到罗马,到公元168年,瘟疫几乎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用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家阿米亚诺斯的话说就是“从波斯边界一直到莱茵河和高卢”。引起这种病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天花病毒(重型天花)。天花病毒是通过被人吸入空气所带的病毒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它引起皮肤发疹,进而变成脓疱,并伴有高烧。它还可能导致出血症。如果安东尼瘟疫确实是天花病毒侵袭了一个从未感染过该病毒的人群,那么,总人口的60%~80%会受到感染,20%~50%的感染者可能会死亡。根据这次瘟疫特征定制的传染病学模型可以估计,这次事件的人口总损失约为25%,这是我们迄今可能得到的最好估计。 [15]
多亏保存了相关的纸草文件,埃及提供了关于这次瘟疫范围及后果的唯一详细信息。根据这些记录,从公元11世纪40—70年代初,卡拉尼斯的法尤姆村的纳税人数量下降了1/3~1/2。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小村庄,人口损失甚至更高,在公元160—170年间,这些地方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0%~90%。虽然人口逃离可能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但逃离本身与瘟疫暴发也脱离不了关系,因为后者往往会引发前者。此外,死亡率数据给人们加强了大量死亡的印象:在索诺帕欧尼索村,仅在公元179年的1月和2月,当地244名登记在册的男性中就有78人死亡。 [16]
我们用埃及中部几个地区的土地实物租金的数据进行考证。在所有有记录的地区,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在疫情暴发前与刚刚暴发的年份之间,土地年租金显著下降。在法尤姆,公元211—268年(已知19个案例)的土地租金的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0—165年(34个案例)的租金分别低62个和53个百分点。在俄克喜林库斯,公元205—262年(15个案例)的土地租金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3—165年(12个案例)分别下降了29个和25个百分点。类似的减少也可以从荷莫波里斯不太坚实的数据中看出。 [17]
以现金表示的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更难以追踪,因为疫情暴发后的总体价格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很可能是这次瘟疫事件造成的混乱结果,包括硬币急剧贬值,其由与之同时发生并很可能有密切联系的财政支出猛增推动。这意味着只有对疫情前后的数据进行调整才能进行直接比较。调整后的比较结果表明,公元2世纪初—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发生了价值从土地财富到劳动力的一致的转移。两阶段间的文献缺口表明实际瘟疫暴发年份缺乏文件记载,这本身就是灾难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志。本次考察,所有的价值都用小麦价格来表示,将这两个时期的小麦价格都标准化为100,由于疫情过后小麦名义价格上涨125%,因此在瘟疫中价值上涨低于125%,瘟疫后的名义价值指数将低于100,反之亦然(见图11.3)。 [18]
劳动契约中记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到接近1/5不等,这取决于雇用的持续时间。然而,完好的记录显示,也能代表劳动力的驴的实际价格上升了一半。相反,诸如油类等非必需食品,尤其是酒的价格相对于小麦的价格下跌了,使得工人能够买到更多的代表更高地位的商品。以油类和酒的价格来衡量的实际工资涨幅远高于用小麦工资衡量的涨幅。土地价值难以比较,因为随着时间变化,我们无法保持土地的质量不变:即便如此,粗略考察后也能看出,它与实际土地租金下降非常类似。这里最重要的是,尽管不同数据集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所有变量的变化都指向一个方向:人口损失后,劳动力获益,土地所有者遭受损失。这和马尔萨斯约束弱化模型一致。此外,小麦的价格(不像没有进口需求的本地酒和油)可以得到罗马帝国大规模小麦出口的支撑:若没有这种支撑,本地需求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或其他大宗货物的价格就可能下跌得更多。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而且模糊了实际价格变化的程度。按照土地价值的数据,实际价格的变化似乎要大得多。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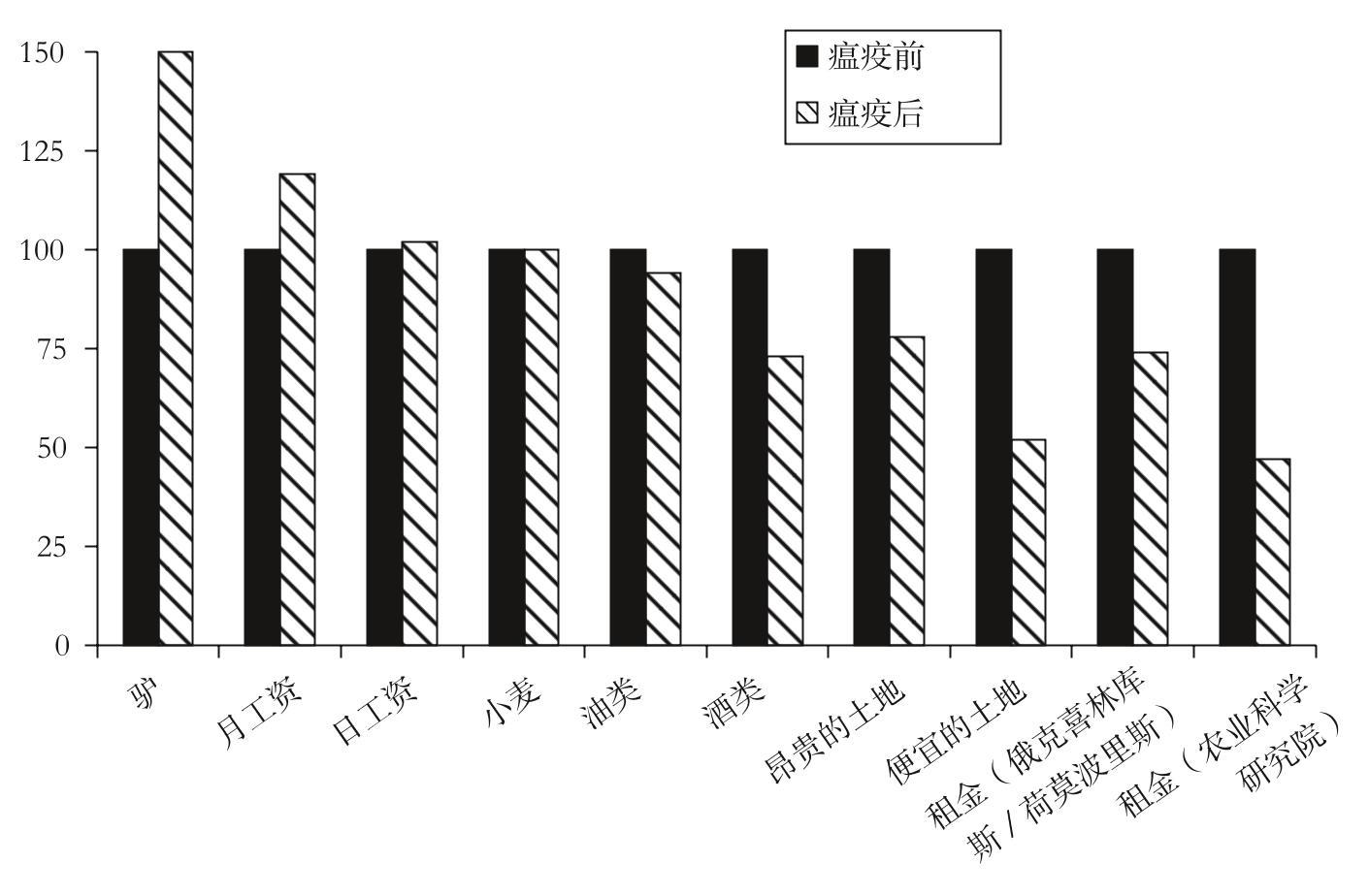
图11.3 公元100年—2世纪60年代和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实际价格与租金变化
以下案例简要说明了瘟疫发生后种植模式的变化。公元158年和159年,在瘟疫到来的前几年,法尤姆的一个村庄塞德尔菲亚大约有4000~4300英亩的土地种谷物,大约有350英亩的土地种植葡萄和果树。到公元216年,可耕地面积缩小到2500英亩,约占之前总耕地面积的60%,葡萄和果树的耕地面积已超过1000英亩,相当于以前种植面积的三倍。因此,尽管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土地种植总面积变少了,但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价值更高的作物。这与我们所看到的黑死病后的种植模式相似,只要是气候允许的地方,就能生产更多的酒,果树种植面积就会扩大,地中海种植更多甘蔗也是这个道理。随着人口数量下降,对基本主食的需求下降了,放弃边际土地提高了收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高端产品,由此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可以被当作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强烈信号。 [20]
考虑到缺乏来自埃及的类似证据,我们不能更加系统地记录这个过程,但它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运动是一致的。学者还发现了佃农和村民社会流动性增大的迹象,农民逃离土地,移民涌入城市,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与瘟疫后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以及城市变得繁荣的情况相一致,正如黑死病过后的情形一样。同样的,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关于瘟疫对不平等影响的可量化的信息。考虑到普遍缺乏与前现代时期发生的瘟疫相关的信息,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前面讨论过的中世纪晚期以及现代早期的意大利保存那么好的数据的情况只是少数。一般来说,瘟疫的矫正效应需要从实际收入的上升和消费模式的改善中推断出来,本例中埃及对这两种情况都有记载。很可能在公元2世纪中叶,埃及就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其人口可能高达700万,堪比1870年左右的水平,而城市化率至少达到1/4,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过1/3。在罗马世界的其他地方,两个世纪的和平促进了人口的长期增长,也考验了农业经济的局限性。在这种环境下,瘟疫的矫正潜力是巨大的。至关重要的是,罗马的劳动力安排是由市场机制控制,地主天然维护自身的财产。这类似于黑死病时期的西欧,而与中世纪晚期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不同。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土地贬值,无法表现出更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21]
在总结我们把瘟疫作为一种矫正力量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并非完全不同的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因素:饥荒。如果大量人口因缺乏食物而死亡,这是否会如瘟疫所造成的结果那样改变幸存者的物质资源分布?答案并不确定,但不太可能是肯定的。首先,饥荒通常不会像大瘟疫那样致命。我们只能说,使死亡率连续两年达到基准死亡率两倍以上(这是定义“饥荒”的一个保守阈值)的饥荒本身十分罕见,更严重的饥荒事件更是极其罕见。单凭这个原因,饥荒控制人口规模的作用就相当有限。报告的饥荒死亡人数往往与证据的质量成反比:越不可靠的记录,其报告的人口损失越严重,这本身也说明问题。此外,饥荒死亡率的估算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需要把移民与瘟疫的影响分开,因为居民已经放弃了饱受折磨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伴随着饥荒。即使是如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受灾人口为1.08亿的特大饥荒事件,死亡人数也只是900万~1300万之间的某个数值,它意味着死亡率不会超过基准死亡率的三倍。我们不知道这场灾难是否会影响不平等程度,而在1770年和1943年的孟加拉国的饥荒中,情况也同样如此,后者发生在战时的压缩时期。 [22]
这一观察引入了命题成立需要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尽管有记录的一些最严重的饥荒确实发生在大矫正时期,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引起了矫正。比如,并不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本身而是当时实施的强制集体化抑制了物质的不平等。中国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饥荒,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再分配以及随后的集体化高潮中,中国就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平等化。 [23]
历史上有两次饥荒因其规模及重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潜力而值得密切关注。其一是1315—1318年的“大饥荒”,它的发生比黑死病早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在这几年里,欧洲西北部异常寒冷和潮湿的天气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同时伴随着导致大量牲畜死亡的家畜流行病蔓延。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前所未有。但这场灾难是否会像瘟疫一样导致价格和劳动力的变化呢?并没有。尽管工人的工资上涨了一点,但不管在城镇还是乡村,物价上涨得更快。由于产量下降抵消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地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比起那些常常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人,在风暴的冲击面前,他们的境况要好得多。 [24]
尽管缺乏数据,但是仅有的信息并不支持存在显著矫正效应的结论。我此前用过的意大利财富分配的记录在时间上稍晚,数据的识别性太弱,无法揭示14世纪上半叶的变化。伦敦和佛罗伦萨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城市工资与物价的福利比率在1300年及1320—1340年间没有任何改善。英格兰农村实际工资数据也是如此。1300—1349年,英国的农村实际工资基本是稳定的,只有在黑死病出现之后,实际工资才持续上涨。从这方面来讲,这两场灾难的后果对比是惊人的。饥荒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矫正效应,这并不难理解:发生大规模死亡只限于几年之内,而且饥荒似乎比瘟疫第一次袭击温和许多。由于减员所造成的就业不足既不持久也不严重,加上受到已有的未正式就业的人口的缓冲,因此不足以预测各次饥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25]
1845—1848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第二个候选案例。这是一种(植物)瘟疫,也是一次食物危机。由致病疫霉菌的传播引起的这次瘟疫导致1846—1848年的马铃薯作物几乎全部腐烂,而马铃薯当时已经成为爱尔兰人不可或缺的食物。多达100万的爱尔兰人失去了生命。再加上部分人移居外国以及出生率的下降,这一事件使得普查人口从1841年的820万减少到10年后的680万。农业劳动力数量迅速减少,从1845年的120万下降到1851年的90万。乍一看,这种人口萎缩与1347—1350年黑死病最初暴发时的人口萎缩相似,但由于这次冲击本身并没有足够的破坏力来引发持久的变化,一位当代英国观察家冷血地说,爱尔兰饥荒的死亡人数在改善整体生活条件方面“难以促成任何好事”。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结果和中世纪晚期反复出现的瘟疫引起的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不仅阻碍人口恢复,也使爱尔兰的人口萎缩:在1850—1914年间,400万人离开了这个岛屿,最终使得人口几乎只有19世纪40年代早期峰值的一半。然而,与瘟疫不同的是,迁移的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十几或二十岁出头。此外,另一个与瘟疫不同的情况是,马铃薯枯萎病导致产量降低从而损害了资本存量。这限制了饥荒在矫正不平等上的价值。 [26]
在某种程度上,由饥荒和随后的移民以及生育率下降而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损失,产生了与大瘟疫相当的经济效益。与早先的趋势不同,饥荒过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都在稳步提升。工资较低的地区出现了更高的人口迁移率,这理应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与此同时,最穷的人离开的可能性小于那些能负担得起旅途费用的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否伴随着资产或收入分配的更大平等。由于逃荒和驱逐,饥荒年代见证了面积最小的——小于1英亩的土地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过程扩大了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60年里,分配变化依然不大:大部分变化发生在底层,小块土地所占的份额又逐渐增加了。拥有1~15英亩土地的现象减少,但拥有更多土地的现象增加了,总体上呈倒退趋势。即使是像马铃薯饥荒及其引发的持续的人口外流那样强大的人口冲击,在矫正不平等的规模上似乎也比不上黑死病所达到的效果。在矫正不平等方面,瘟疫无疑是最有力的。 [27]
目前,我们对瘟疫在矫正不平等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是比较新的。尽管黑死病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其他人口灾难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直到最近才被研究。来自埃及和安东尼瘟疫及查士丁尼瘟疫相关的价格变化的证据,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分析,对早期墨西哥的实际工资以及意大利北部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的研究,都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才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增多,进一步证明材料出现的希望增加了,这些有待人们去收集并解释。关于黑死病时期及其余波的档案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我们还需要研究被证实和安东尼瘟疫、黑死病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主要瘟疫的矫正效应。
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幸存的信息可能永远不足以揭示实际收入和不平等的问题。塞浦路斯大瘟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大规模的瘟疫在公元3世纪50—60年代肆虐于罗马帝国,其对人口统计学上的影响极富戏剧性。当时的观察家、帝国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城主教狄奥尼修斯写道,“这些持续的瘟疫……这些对人类的巨大毁灭”使得亚历山大市的人口大为减少,14~80岁的居民人数比瘟疫前40~70岁的居民人数少得多。这一数字据说来自公众玉米救济登记册,应该不是完全虚构的。言下之意,死亡的规模是惊人的:按照当时的典型寿命统计表测算,损失了超过60%的城市人口。人们无法得到当时实际工资的数据,更不用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数据了。即便如此,在公元3世纪50年代,埃及两个地区的农村工人的名义工资突然大幅上涨,可能反映了这场瘟疫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 [28]
一旦进入前基督教时代,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更少了。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减少导致实际工资上涨的最早证据。公元前6世纪70年代,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建造巴比伦王宫的工人可以得到450~540升大麦的工资,或者每月约5舍客勒的银子,相当于日工资为12~14.4升小麦,类似于可买11.3~12升小麦的现金工资。小麦工资相对上涨可从以下数据证实,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的那波尼德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小麦工资为每天9.6~14.4升,中间值为12升。所有这些值远高于每天3.5~6.5升这个看来是前现代时期正常值的核心范围,也高于公元前505年左右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工资,当时的工人仅得到相当于7.3升小麦或更少的工资。巴比伦后来的实际工资甚至更低,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低至4.8升。 [29]
新巴比伦的这种暂时性的价格上升目前还未得到解释。一个乐观的观察者可能会设想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高度劳动分工以及货币化加快所驱动的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短暂繁荣,这些都被证实了。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亚述帝国的血腥崩溃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收益减少也可能解释它。后者在巴比伦最南部引起的人口损失堪比一场瘟疫,不能不成为这场灾难性冲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实际工资的快速下降似乎也很难从纯粹的人口复苏方面得到解释。
尽管我们的认识中存在如此多的空白,曾经主要甚至完全是由黑死病引发的矫正过程,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反复发生的现象。本章所提出的所有研究结果都趋于支持一个考虑了制度框架的马尔萨斯人口数量矫正论。这些矫正事件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人口的大量损失,在每一个主要案例中都有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矫正效果的短暂是另一个共同点,因为人口恢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抵消了这些好处。因此,瘟疫是一种既极其残酷又最终不可持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压缩机制。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可以与已经考察过的其他有效矫正进程(大规模动员战争的牺牲,改朝换代的残酷革命以及大规模国家崩溃的破坏)相提并论。所有这些事件都通过巨大的流血牺牲和人类苦难矫正了物质上的不平等。我们的矫正四骑士论现在已经完成了。
通过对四骑士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严格分离历史上的主要矫正机器有助于使讨论结构化,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无法更清楚地了解过去实际生活中更加混乱的方面。通常情况下,两名或更多的“骑士”会作为不同的矫正机制形成合力,并相互作用。17世纪德国南部奥格斯堡市的经历为说明不同“骑士”的复合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主要影响因素是战争和瘟疫。 [30]
作为欧洲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中复苏的一个引擎,奥格斯堡曾是现代早期德国南部的经济中心之一。它的人口从1500年的20000人增长到1600年的48000人,成为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随着财富的扩张和分配的日益不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剧了资源不平等。这个城市对所有城市家庭定期评估、征收财富税,因而存在详细的记录,形成关于实际资产及其分配的一个相当准确的代理变量。我们需要考虑几个易混淆的变量。即使是那些被记录为没有应税财产的居民,也会拥有一些个人财产,这些财产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测度的不平等程度。与此同时,每个家庭的一般豁免额为第一个500基尔德的现金收入——在税率为0.5个百分点时,这等于豁免2.5基尔德税额,比1618年收入最高的前1/5以下的人的收入都多。珠宝和银器同样是免税的。所有这些税收优惠都对富人有利,且一定多于对未上税穷人的微薄财产免税额的补偿。总的来说,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似乎相当具有代表性。数据记录了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由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财富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的0.89(见图11.4)。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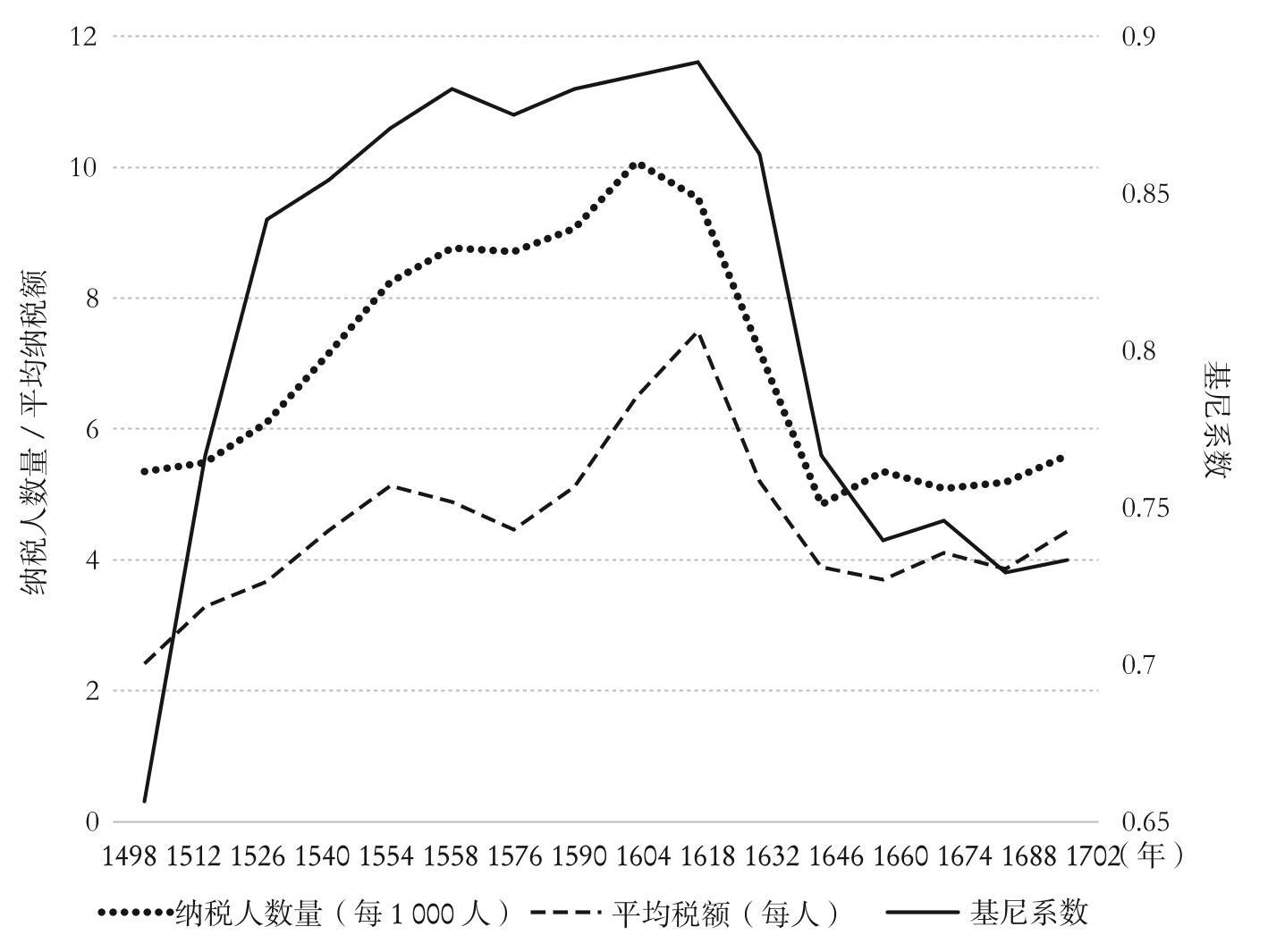
图11.4 奥格斯堡的财富不平等:纳税人的数量、平均纳税额以及纳税的基尼系数,1498—1702年
1618年经济阶层分层形势紧张:最富有的10%的家庭支付了91.9%的财富税,基尼系数达到0.933。即使是特权阶层内部也有很大的分层:最富有的1%的人,包括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几乎贡献了财富税总收入的一半。2/3的注册纺织工、建筑工人和89%的全日制劳动者根本不交任何税。在奥格斯堡社会的底层,我们发现大约有6000名贫困阶层,包括约1000名流浪乞丐、1700名主要依靠救济的人和3500名部分依靠救济生活的人。只有2%的群体是富裕的,1/3人口处于中等水平,2/3是穷人(至少一半的人处于维持生计、勉强糊口的边缘),没有迹象表明以经济增长为支撑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相反,我们观察到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就像在前一章中所考察的众多其他城市人口一样。 [32]
这就是30年的战争开端时的情形,复杂而漫长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德国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大面积的房屋和资本被破坏,人口损失巨大。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瘟疫的复发并与之相随,促进了一种相对较新的疾病——伤寒的传播,这进一步提高了死亡率。在战争初期,奥格斯堡市并不是直接的目标,只是间接地受到了影响,最显著的影响是货币贬值。用劣质货币支付战争费用的办法引发17世纪20—30年代物价膨胀,最初只上升了一个数量级。更低层级的人似乎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影响,富有的商人通过购买那些陷入困境的中间阶级所拥有的房地产得到额外的利益。比较1625年和1618年的税收贡献,有更多的商人支付比以前更多的税收,他们的贡献增加了3/4,这是财富在这一群体最成功的成员中快速聚集的一个标志。作为“老贵” [01] 代表的贵族中,赢家和输家各占一半。精明的商业资本所有者最善于利用与战争相关的货币动荡。穷人变得更穷,部分较为富裕的中等居民却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赢家包括金匠和旅店老板,这要归功于他们能直接接触到珍贵的金属和食物等稀有物品。 [33]
然而,当瘟疫和战争袭击奥格斯堡时,所有这些好处很快就消失了。瘟疫带来了第一次大的打击,这是一波从阿姆斯特丹横扫德国和意大利的更大疫情的一部分。1627年10月,战争通过驻扎在城市中的士兵把瘟疫引入奥格斯堡。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瘟疫继续肆虐。1628年,每4万~5万的居民中就有约9000人失去生命。1625—1635年间,福利支出的空间分布和奥格斯堡人口缩减的分布十分匹配,这表明瘟疫不匀等地杀死了穷人。1632年和1633年,瘟疫的第二次暴发具有同样的效果。这种不平衡有助于强化这个城市整体的矫正效应。由此产生的混乱也降低了流动性。1629年,该市对债权人实施了一种估值折扣,以降低前几年贷款的高额利息。债权人如果提起诉讼,其处于裁定期间时将会被暂停支付任何利息或本金,因此债权人都对此望而却步。 [34]
瑞典军队于1632年4月抵达。尽管如此,和平接管期间高昂的占领成本还是加重了当地天主教家庭以外的居民的负担。在这座城市里,大约驻扎了2000名士兵,还要支付修筑大规模防御工事的费用。政府引入了特别税,包括适度累进的人头税。城市面临破产,市政债券的利息也完全停止了支付。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受害者。在占领期间,死亡率再次飙升,这一次是因为1632年的瘟疫复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由天主教势力封锁造成的饥荒。 [35]
1634年9月,瑞典在讷德林根战役中战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帝国军队几乎立刻就包围了奥格斯堡。这场围困持续了将近半年,直至1635年3月,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穷人遭受的损失最大:记录者雅各布·瓦格纳讲述了那些只能吃动物皮、猫、狗和人类尸体的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挖墓者报告说,有些尸体胸部和其他身体部位的肉不见了,一些市民啃着躺在街道上的死去的马的骨头。死尸和将死之人的恶臭笼罩着这座城市。与此同时,瑞典驻防部队对当地管理委员会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交出巨额的军税:第一次就征收了相当于一整年的税。只有富人才有希望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36]
1635年3月,驻防部队接受了使其秘密离开的投降条件,但这些条件迫使该城市为帝国军队支付一大笔费用和赔款。在天主教家庭承担了此前税收的冲击之后,现在轮到有财产的新教徒来付出其所剩财产的一部分。同年进行的人口普查部分地揭示了形势。房地产的分配几乎没有变化,但房价已大幅下跌,因为租金下跌,待售房屋状况不佳,潜在的投机者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无法获得被低估的资产。4年后,雅各布·瓦格纳声称,房价已跌至占领前价格水平的1/3,工匠的工作坊也空了一半。该市的精英对这些负担报怨诸多。1636年,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纽伦堡面见哈布斯堡皇帝,他们声称奥格斯堡剩余的1600个新教徒家庭由于被迫花费大量的钱来支付军队驻扎和其他费用而变得极度贫困。1840年,在军队撤退一年之后,另一个公使馆证明,在过去的5年里,奥格斯堡的新教徒必须支付8倍的税,并且损失100万以上基尔德,如果这是真的,其损失将相当于该市年收入的许多倍。 [37]
到1646年,受瘟疫和战争的累积影响的资产负债表不忍卒读。1616—1646年,奥格斯堡的人口下降了50%~60%,类似于其他受影响严重的城市,如慕尼黑、纽伦堡和美因茨。然而,其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阶层两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见表11.1)。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成比例地下降了:4/5的纺织工家庭消失了,不仅是因为死亡或移民,还因为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职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穷,这一损失,加上穷人之间的极度内耗,这些曾在城市居民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的居民死亡,导致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使得不平等状况得到矫正。 [38]
表11.1 1618年和1646年奥格斯堡按税级划分的住户比例和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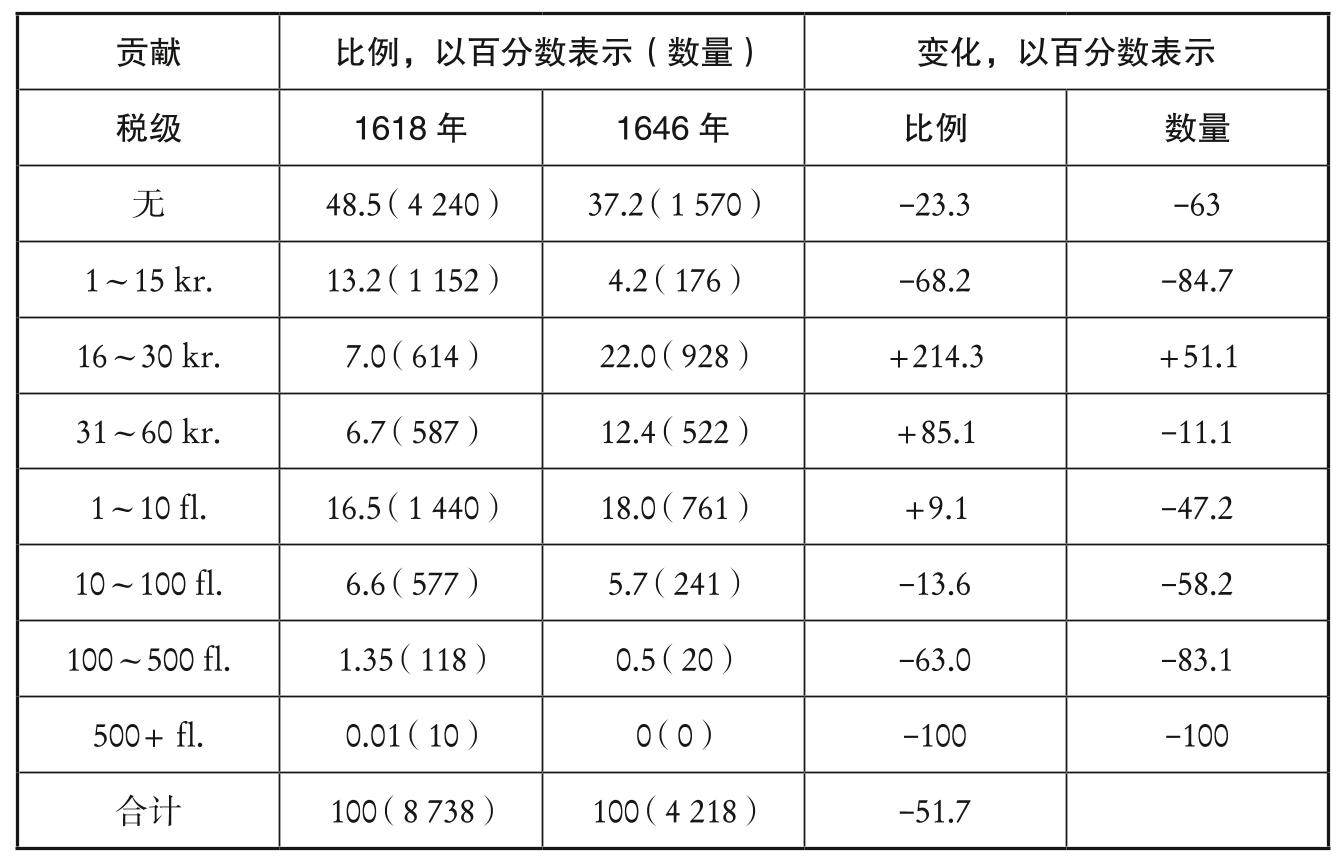
Kr.:十字硬币;fl.:基尔德
城市的社会上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超级富豪家庭现在仅仅算得上富有,而那些仅仅是富有的家庭的数量减少了5/6。那些舒适或中等收入的家庭数量减少了一半,但占总人口(总量大大减少)的比例大致保持了稳定。即使在穷人和赤贫的比例下降的情况下,收入阶层中那些稍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在激增。整体的矫正效应是巨大的。
这些变化伴随着甚至比人口数量下降还要严重的应税财富的减少——大约下降了1/2~3/4。根据财富十分位数进行的税收收入分解显示,税收收入的急剧下降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10%的人的损失造成的。在1618年,最高十分位数的人贡献了91.9%的财富税,1646年这一比例是84.55%。从绝对数来看,这一群体的支出已从52732基尔德降至11650基尔德,占财富税收总下降额的94%以上。由贵族家庭所代表的“老贵”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平均税收贡献减少了近4/5。 [39]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1646年,法国和瑞典军队对该市发动第二次包围,虽然失败了,却使年死亡率翻了一番。当年,由当地商人组织的一场纪念活动哀叹因战争、封锁和军队驻扎引起的进攻、掠夺以及新的或更高的关税而导致的商业衰退。总之,这些因素被认为减少了投资和信贷的机会,损害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1648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现了另一个被围困的风险,2400名士兵驻扎在这个城市,直到最后和平谈判结束才离开。 [40]
这个幸存下来的城市不过仅有以前繁荣的影子。它的人口减少到不及战前的一半,它目睹成千上万的最贫穷的居民被瘟疫和饥饿折磨致死、拥有资本的精英被榨干。巨大的财富消失,较小的财富也减少很多。房地产失去价值,贷款变得一文不值,安全的投资机会减少:简而言之,资本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后,严重的人口损失增加了对幸存劳动者的需求,改善了劳动阶级的状况,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先前遭受的赤贫处境。到战争结束时,(被代理的)应税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从超过0.9降至约0.75,虽然仍然很高——甚至比黑死病后的水平要高得多,但没有像以前那样极端了。这种矫正效应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且在1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一直持续着。 [41]
*
奥格斯堡经历了西欧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之一,其间又发生了继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瘟疫,它的情况可能显得特别。然而,我们观察到的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矫正的推动力量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大规模的暴力和人类的苦难是剥夺富人财富和减少劳动人口从而使幸存者的状况明显好转起来所必需的。社会阶层的顶端和底部的不同形式的损耗,都汇聚在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上。正如我们在本书此部分及前三部分所看到的,相似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从铜器时代的希腊到“二战”中的日本,从黑死病蔓延中的英国到大西洋交换中挣扎的墨西哥。尽管这些案例跨越人类历史和几大洲的记录,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源不平等的大幅下降依赖于暴力灾难。这就提出了两个迫切的问题:没有其他方法来矫正不平等了吗?现在有吗?现在,是时候去探索比我们“四骑士”的血腥程度更低的替代品了。
[1] See Diamond 1997: 195–214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Columbian Old and New World disease pools.Crosby 1972 and 2004 are classic accounts of the Columbian exchange.For a very brief summary, see Nunn and Qian 2010: 165–167.
[2] The following survey is based on Cook 1998.My section caption is a quote from the Mayan Chilam Balam de Chuyamel in Cook 1998: 216.Quotes: 202, 67.
[3] For the debate, see McCaa 2000; Newson 2006; Livi Bacci 2008 (who emphasizes the multiplicity of causal factors).Arroyo Abad, Davies, and van Zanden 2012: 158 note that the quadrupling of real wages in Mexico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is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 a population loss of about 90 percent, a tantalizing if inconclusive bit of support for very high mortality estimates; see herein.I follow McCaa 2000: 258.
[4] Williamson: 2009: 15; Arroyo Abad, Davies, and van Zanden 2012.Fig.11.1 from 156 fig.1, using the data at http://gpih.ucdavis.edu/Datafilelist.htm#Latam.
[5] Arroyo Abad, Davies, and van Zanden 2012: 156–159.
[6] Contra Williamson 2009: 14, it is not obvious a priori that Spanish conquest would have greatly raised inequality from pre-Columbian levels, at least no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ighly exploitative and stratified Aztec and Inca empires.
[7] The literature is fairly larg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recent survey is Stathakopoulos 2004:110–154, to be used alongside the case studies in Little 2007.Specifically for the initial wave,see also the convenient discussion by Horden 2005.The quote in the section caption is from ancient sources referenced in Stathakopoulos 2004: 141, and the quote is from Procopius,Persian War 2.23
[8] Symptoms: Stathakopoulos 2004: 135–137; DNA: Wagner et al.2014; Michael McCormick,personal communication.Corroborating evidence from a second site is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published.
[9] Stathakopoulos 2004: 139–141 (numbers).McCormick 2015 survey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mass graves from this period.John of Ephesus: Patlagean 1977: 172.Quote: Novella 122(April 544 CE)
[10] Economists: Findlay and Lundahl 2006: 173, 177.Egyptian evidence: Fig.11.2 is constructed from Scheidel 2010: 448 and Pamuk and Shatzmiller 2014: 202 table 2.
[11] Scheidel 2010: 448–449; Sarris 2007: 130–131, reporting on Jairus Banaji’s unpublished Oxford dissertation of 1992.
[12] For the Cairene data, see Pamuk and Shatzmiller 2014: 198–204, and see 205 for the calculation of wheat wag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250 working days per year.Baghdad: 204 fig.2.Consumption basket: 206–208, esp.207 fig.3.
[13] Pamuk and Shatzmiller 2014: 209 Table 3A (outbreaks), 216–218 (Golden Age).
[14] Bowman 1985; Bagnall 1992.
[15] For this event, see esp.Duncan-Jones 1996; Lo Cascio 2012.The quote in the section caption is from Orosius,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7.15.Ammianus, History 23.6.24.Smallpox: Sallares 1991: 465 n.367; Zelener 2012: 171–176 (model).
[16] Duncan-Jones 1996: 120–121.
[17] Scheidel 2012: 282–283, updating Scheidel 2002: 101.
[18] Fig.11.3 is taken from Scheidel 2012: 284 fig.1, mostly building on Scheidel 2002: 101–107.
[19] 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在瘟疫前和瘟疫后,消费篮子的整体购买力没有差异(根据Scheidel 2010:427–436计算而得)。不同程度的外部需求可能也解释了与查士丁尼瘟疫相比,安东尼瘟疫后小麦价格上涨乏力的原因,如图11.2所示。此外,由于病原体的不同,尤其是持续的时间不同(几十年与几个世纪),安东尼瘟疫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少。
[20] Sharp 1999: 185–189, with Scheidel 2002: 110–111.
[21] Scenario: Scheidel 2002: 110, with references.Population: Scheidel 2001: 212, 237–242, 247–248 (Egypt); Frier 2001 (empire).Borsch 2005: 18–19 notes similarities to western Europe.
[22] Watkins and Menken 1985, esp.650–652, 665.For India, see herein, chapter 5, p.157.
[23] See herein, chapter 7, pp.219 and 224–227.
[24] Jordan 1996: 7–39 (famine), 43–60 (prices and wages), 61–86 (lords), 87–166 (commoners).
[25] For wealth shares, see herein, Figs.5.4–7; for welfare ratios, see herein, Figs.5.1–2.Clark 2007b: 132–133 table A2 computes rural real wages.If the mean real wage from 1300 to 1309 is standardized at 100, it averaged 88 in 1310–1319, 99 in 1320–1329, and 114 in both 1330–1339 and 1340–1349 but 167 in 1350–1359, 164 in 1360–1369, and 187 in 1370–1379.A clear rupture occurred between 1349 (129) and 1350 (198).For the scale of famine mortality, see Jordan 1996: 145–148 (maybe 5–10 percent in urbanized Flanders in 1316).
[26] On the famine, see Ó Gráda 1994: 173–209, esp.178–179, 205.“Hardly be enough”:Nassau William Senior according to Benjamin Jowett, quoted from Gallagher 1982: 85.ÓGráda 1994: 224, 227 (emigration), 207 (capital stock).
[27] For rising real wages and living standards, see Ó Gráda 1994: 232–233, 236–254; Geary and Stark 2004: 377 fig.3, 378 table 4.Earlier trends: Mokyr and Ó Gráda 1988, esp.211, 215, 230–231 (rising inequality); Ó Gráda 1994: 80–83 (no sign of a sharp fall in real wages); Geary and Stark 2004: 378 table 4, 383 (some increase followed by stagnation).Landholdings: Turner 1996, esp.69 table 3.2, 70, 72, 75, 79 table 3.3.
[28] Harper 2015b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Parkin 1992: 63–64 (Dionysios); Freu 2015:170–171 (wages).
[29] Jursa 2010: 811–816; see also Scheidel 2010: 440–441.For this period, see also herein,chapter 1, p.48.
[30]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the monumental study by Roeck 1989.The quote in the section caption(790) is from the Augsburg chronicler Jacob Wagner.
[31] For the registers, see Roeck 1989: 46–62.Fig.11.4 is based on Hartung 1898: 191–192 tables IV-V; see also van Zanden 1995: 647 fig.1.
[32] Roeck 1989: 400–401 (10 percent), 432 (1 percent), 407, 413–414 (workers), 512 (no middle class).Roeck’s Gini estimate for 1618 is more precise than the lower one derived from Hartung 1898.For falling real wages elsewhere, see herein, Fig.10.1–2.
[01] “老贵”(old money)一般指财产来自继承的富人。“新富”(new money)指靠自身努力致富的人。——编者注
[33] Roeck 1989: 553–554 (inflation), 555–561 (real estate), 562–564 (winners).
[34] Roeck 1989: 630–633, 743–744, 916.
[35] Roeck 1989: 575, 577 (debt service), 680–767 (Swedish occupation), esp.720–722, 731–732, 742.
[36] Siege: Roeck 1989: 15–21.Cannibalism: 18 and 438 n.467.
[37] Roeck 1989: 765 (garrison and indemnity), 773 (Protestants), 790 (real estate), 870, 875 (legations).
[38] Roeck 1989: 880–949 (population losses: 881–882).Table 11.1 based on Roeck 1989: 398 table 28, 905 table 120.
[39] Registration peculiarities suggest that intervening changes in how fortunes were assessed obscure even greater loss of actual wealth: Roeck 1989: 907–908.Shares: 909 table 121 (top decile), 945 (patricians).
[40] Roeck 1989: 957–960 (siege), 307, 965 (deaths), 966 (investment), 973–974 (1648).
[41] Roeck 1989: 975–981 for a final summary.Persistence: herein, Fig.11.4.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有章节读起来都相当令人沮丧。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要付出相对人们的承受能力而言很高的代价才能获得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显著缩小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服务于这一结果。大多数战争很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也同样可能提高了它,这取决于一国站在哪一边。内战产生了相似的不一致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可能扩张而非缩小不平等程度。军事总动员成为最有前景的平等化机制,因为特殊的暴力产生了特别的后果。然而,尽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战争的普遍现实,这种现象及其平等化的后果在早期却很少见:古希腊可能是唯一的先例。同时,如果最猛烈的战事最有可能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那么最激烈的革命就更会如此:归根结底,20世纪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调整。与此对应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缺乏雄心的冒险活动只能产生较弱的效应,历史上大多数的群众起义则根本无法平等化贫富差距。
国家的衰落成为一种更“可靠的”矫正方式,随着富裕和强权阶层被扫除,不平等被消灭。正如大规模动员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一样,平等化过程也伴随着人类深重的痛苦和灾难,这同样也适用于最具灾难性的传染病:尽管最大规模的流行病具有强大的矫正力量,我们却很难再想到一种比疾病更加糟糕的治愈不平等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矫正的程度在过去是暴力程度的函数:施加的力量越多,产生的矫正效果就越大。尽管这不是一个铁律,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暴力的,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产生矫正效果,不过它可能接近我们大体上期望得到的一个一般性前提。毫无疑问地,这是一个极其悲观的结论。但这是唯一的方法吗?暴力总是像战争一样成为矫正的源泉吗?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说法,暴力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吗?有没有和平的替代性方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分析了很多种可能的候选方案,尤其是土地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我通过考察一些反事实的替代方案得到以下问题的结论:在大规模暴力冲击缺失的情况下,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平等状况将会如何发展? [1]
土地改革值得优先考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人依靠土地为生,同时耕地一般代表了私人财富的数量。在300多年前的法国,土地代表了所有资本的2/3,而在英国这一比例大约是60%。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并非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至少这几百年来的典型事实就是如此。土地分配因此成为不平等程度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整个有史料记载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次将土地所有权变得有利于穷人的尝试。土地改革并非天生就与暴力相伴: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会限制人类社会通过和平地调整土地所有权使穷人受益。然而在实践当中,情况常常会不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成功的土地革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依赖于暴力的实施或者威胁。 [2]
我们已经在第7章中探讨了最为显著的例子。尽管在古巴这样的一些例子当中,暴力是潜在的而并非是很明显的,但苏联革命的暴力本质和矫正力量都毋庸置疑。随着“冷战”结束,这一类型的激进式土地革命逐渐消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是一些有记录的最近的案例。从那时开始,津巴布韦是唯一重要的强迫性土地分配的例子。在该国,土地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以较为温和的步伐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加快速度,大约1/10的农业土地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转移到70000个大多数是穷苦黑人的家庭中。激进的土地改革开始于1997年,当时解放战争的退伍军人通过占据白人大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发起了“土地入侵行动”。结果,另外1/8的农场土地被标记为强制性征收。到目前为止,大约90%在1980年由6000个白人农场控制的土地被分给25万个家庭。规模较大的白人拥有的农场在所有土地中的比重从39%降到0.4%。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从少数精英到贫困家庭的巨量的净财富转移。自1997年开始的更为激进的第二阶段土地改革,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退伍军人的暴力骚乱。当穆加贝政府无法兑现对福利和财政支持的承诺时,退伍军人和那些在他们帮助下动员的群众不仅挑战了白人定居者,也挑战了政府,从而迫使穆加贝允许对于白人拥有的商业性农场的暴力掠夺。在最初试图控制这场运动之后,穆加贝于2000年通过瞄准这些农场并且实施保护占领者的措施加入其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20世纪早期墨西哥革命的回响,那时当地对不动产的侵占同样也驱动了政府的行为。本地的暴力行为是拓展土地再分配范围和财富平等化的关键方式。 [3]
历史上许多土地革命都是战争的结果。在第4章中,我回顾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在美国占领下,日本的土地改革涉及实际上毫无补偿的没收和全国范围内彻底的土地所有权的重构。这是“二战”之后的时代中一个崭新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外国占领者从来没有促进一种再分配过程的计划。中欧地区的苏维埃式秩序是占领军发起的主要平等化形式。从历史角度来看,战争也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为土地改革提供了动力。为回应战争的威胁进行的改革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机制,通常被用作支撑一国的军事能力。
根据一些相关记载,公元645年在日本发生的大化革新可以被视作这一过程的一个早期例子。效仿近邻中国在隋朝和唐朝时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土地平等化的措施,农地被测量并在相同大小的小块土地组成的网格体系中被组织起来。他们基于有生产力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将肥沃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单个的家庭,同时也安排了周期性的重新配置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被分配的这些地块,严格说是公共的,也就意味着是不可转让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确定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多大范围或者多么实际地被实施了。此处重要的是,在国内外战争的威胁下,他们是在进行改革的背景中实施的。在公元7世纪60年代,对朝鲜的介入使得日本陷入与中国的对立当中,并且提高了日本对于相邻的强权国家的军事入侵的担忧。由此导致的军事化,被672年和673年关于王位继承的壬申之乱打破。日本首次人口普查在689年进行,并且引入了对所有成年男性的征兵制。战争的威胁似乎为用于压制本地精英群体而扶持一般民众之间紧密团结设计的改革提供了动力,这也为军事动员做好了准备。 [4]
用沙皇俄国的情况来分析会更清楚一些。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的一个月之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做出承诺:“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同等正义的。”在5年内实施的包括解放农奴在内的各项改革,意在用普遍征兵制支撑更大规模军队建设。农民现在可以拥有他们耕作的小块土地。然而,这一平等化措施由于农民有着要支付等同于这块土地价值75%或者80%金额的补偿金的义务而受到阻碍。政府债券为此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民不得不在超过49年的时间内每年偿还6%的利息,这就在长时间内榨取了他们的资源,因而常常使得他们只能获得比之前耕种的地块更小的土地份额。当一些人获得了土地而另一些人没有的时候,差异化程度就增加了,较为贫穷的农民变得无产阶级化,同时更为富裕的家庭与其他人的界限更加分明了。紧随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出现的骚乱触发了另一轮的土地改革。在这个时候,农民依然仅仅只拥有所有土地的3.5%。他们拒绝再提供补偿性的支付,进行罢工并且攻击各种不动产,破坏了超过1000座的庄园房屋。出于对这种暴力活动的回应,所有未完成的补偿性支付都被取消了,同时农民被赋予将其土地作为可继承性财产的权利。结果是,在“一战”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已经变成了农民的财产。即使是这样,在少数大的地主和大量小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持续存在的财富差距依然提高了整体上的土地不平等,同时,干重活的马匹的分布也变得比早期更加不均等了。 [5]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以恶化的不平等状况为结局的战争驱动下的土地革命有着很长的历史。拿破仑战争在不少国家都引发了土地革命,在较长的时间内带来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普鲁士,1806年战争失败的冲击促进了下一年农奴制的废除,同时尽管佃户被允许从贵族和皇室那里购买土地,价格还是非常高的,较大的地主——容克地主强化了他们对土地的控制,并且一直保持主导性的位置,直到1945年,共产党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了所有大型的地产。在西班牙,拿破仑战争也同样促进了自由化。限定继承权在1812年被废除,同时公共土地也被拿出来进行销售,然而接下来的内战导致土地所有权更大程度的集中——葡萄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奥地利,正是1848年的革命迫使政府确保农奴不再受到封建性义务的约束:名义上的这种法律关系在18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引入了,但直到这个时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法律才得到合理的执行。被转让的土地的赎买价格被设定在其年度收益的20倍的水平上,并且在农民、政府和地主(他们因此被没收了其土地财富的1/3)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是一个用和平购买的方式对民众的动乱做出回应的例子。 [6]
其他由战争激发的改革尝试更为激进,但也被证明是短命的。创立于1901年的保加利亚农民国家联盟在联络农村民众上一直是不成功的,直到“一战”战败带来的投降、政治动乱和领土损失所产生的重大冲击在1920年使他们得以执掌政权。其土地改革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土地的所有权以30公顷为限,超出此范围所持有的土地要按照递减的比例(补偿水平随着规模而缩减)强制性地被卖出,并且转移到无地农民或者土地较小的持有者手中,同时教会土地和通过投机和发战争财获得的财产被充公。这些措施很快就引发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暴力回击,导致政府被推翻。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危地马拉,战争效应以一种更为间接的形式发挥出其作用。在战争中的那些年份里,德国的咖啡市场的消失以及美国的压力使得很多德国人拥有的咖啡种植园被国有化,大地主的压迫性统治被弱化。这就为1952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府实施农业改革开辟了道路:大地主的土地被进行再分配,通过政府债券对原来的所有者进行补偿,这种债券是根据他们过去所填报的、一般而言低估的税收申报来定价的。到1954年,经过一种和平且有秩序的改革,40%的农村人口已经获得了土地。然而在同一年发生的一场政变建立的军政府取消了这场土地改革并重建了压迫制度。在接下来的漫长内战中,总计15万人丧生。到20世纪90年代,3%的地主掌握了全国所有土地的2/3,90%的农村人口几乎完全没有土地。这一过程中的暴力以不同方式体现其特征:首先是以促进变革的方式,然后是以一个被证明无法应对暴力干涉和镇压的和平政府缺席的方式。 [7]
在其他一些关系到内部或者外部的潜在暴力的例子当中,土地改革是突然发生的。反共产主义是其中一个特别强烈的动因。“二战”结束后,韩国的土地不平等程度非常高:少于3%的农村家庭拥有所有土地的2/3,而58%的家庭没有任何土地。接下来发生的土地改革其实是出于对朝鲜的恐惧,后者早在1946年就在其控制的朝鲜区域没收了私有土地,这可能动员起南部的本地农民。美国的支持,以及参加1948年第一次选举竞争的所有党派都承诺的土地改革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征收和再分配。首先,所有的日本殖民地的财产被查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韩国将私人产权的上限设定为3公顷的优质农田,超过的部分则通过没收或者以很小的补偿(年租金的1.5倍)后售出的方式被转移给其他农民,同时对于依然在别人的土地上耕种的佃农,其地租被限定为较低的水平。略微超过一半比例的土地改变了其所有者。再分配的效应是巨大的:地主丧失了其收入的80%,处于底层的80%的农村家庭获得了20%~30%。到1956年,最富有的6%的地主只掌握18%的全国土地,佃农的比重从49%下降到7%。土地所有权的基尼系数,从1945年高达0.72或者0.73,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0.3的水平。朝鲜战争的后果放大了土地改革的矫正效应:因为大多数的工业和商业财产都已经被摧毁,恶性通货膨胀使得这些补偿毫无价值,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完全消失,同时出现了一个高度平等化的社会,并在此后通过受教育机会的扩大而得到维持。在这个例子当中,对战争和革命的关切被真实发生的总动员性的战争取代,在第5章中我们描述了与之类似的具有平等化后果的例子。 [8]
对革命和真实战争的忧虑同样也在越南共和国聚集,在美国的鞭策下,它于1970年实施了土地改革:所有租佃的土地都将被转交给耕种者,他们将免费得到一定大小的土地;土地所有者得到了补偿。在三年之内,这项改革就得到了实施,土地租佃的比例也随之急剧下降——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从60%变成了15%。
1921年在罗马尼亚进行的土地改革可能是这种遏制战略的一个早期例子:它使得获得征用土地的较为贫穷的农民和小地主受益,有时这被认为是由人们对可能从邻近的苏联散播过来的革命的恐惧引发的。美国在1960年建立了“和平联盟”以应对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推销土地改革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智利就是候选人之一:在早期实行了一些缩手缩脚的举措之后,对于1964年选举失败的关切导致右翼和中间派的联盟支持更大范围的土地改革。到1970年,很多大的庄园都已经被没收,但为此支付的费用是有限的。阿连德的左翼政府取得了更多的进步,直到其被1973年发生的政变推翻。尽管这事件阻碍了整个进程,但是到这时,1/3的土地已经为小地主所拥有,而10年之前这一比例只有1/10。 [9]
面对秘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存在农村暴力的情况,1968年的军事政变的领导者强烈反对该国传统的寡头政治。经受过美国反游击战理论训练的他们选择将土地改革作为延缓全面内战爆发的工具。几年之内,大多数大型的庄园都已经被没收,全国土地的1/3已经被转让,1/5的农业劳动力都从中受益。大地主的权力被打破主要使得军人和普通农民,而非穷人获益。类似的一些被激发的措施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得到实施。在萨尔瓦多,游击战爆发一年之后,在美国的鼓励和财政支持下,军政府在1980年发动了土地改革。 [10]
大约10年以前,对革命的恐惧同样也促使埃及发生土地改革。土地的分配曾经非常(尽管不是极端的)不平衡,最富的1%的地主控制了1/5的土地,最富有的7%的地主拥有的土地比例达到2/3。租佃的比例很高,同时佃农的地位与劳工一样糟糕。在1952年纳赛尔的军事政变发生之前的10年间,埃及已经被动荡环境撕裂,其间更换了17届政府,还伴随戒严、罢工和骚乱。统治阶级的成员已经成为暗杀行动的目标。新政府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开始土地改革。与同时期的东亚国家一样,美国为其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以限制改革的影响。农业部长赛义德·马雷,援引了这些恐怖的事实来为改革提供辩护:
我们记住了1952年7月革命以前的一些日子;我们记得埃及的村落如何由于危险的焦躁氛围而变得动荡不安;我们记得那些导致杀戮和财产毁坏的事件……难道这些大地主更愿意暴露在这些骚乱带来的狂风下,利用欲望和贫困为自己谋利,直到其变成摧毁一切的狂风骤雨?
私人土地所有制被设置了上限,但是土地所有者得到补偿,同时国家允许土地的受让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一种与1861年的沙皇俄国时一样的机制向国家进行偿还。由于支付的金额要比此前的租金低得多,所以这种安排是以一种对农民有利的方式运作的。1/10的土地改变了所有者,财富的分配受到的影响要比收入分配受到的影响小。在伊拉克,政变和复兴党的统治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同时集体化在20世纪60—70年代显著降低了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程度。1971年在斯里兰卡发生的一场失败的革命,虽然被认为牺牲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但没收私人以及后来一些企业超过给定限度的土地的做法也促进了在次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再一次受到暴力的驱使,这种干预代表了一种与所有独立以前的历届政府未能解决土地不平等问题的做法的彻底背离。 [11]
所有这些例子都一致指出暴力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还是潜在的,它们都带来了有意义的土地改革。然而,最终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土地改革在降低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成效乏善可陈。对于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27个土地改革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的案例当中(21个,或者说78%),土地不平等状况要么大体上保持不变,要么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任人唯亲也可能破坏和平的土地改革。在20世纪60年代的委内瑞拉,民主选举的政府将1/10的农村农地再分配给1/4的无地穷人——其中一半来自没收,另一半来自国有土地。在那个时候,该国正在从一个主要依赖农业经济向建立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城市经济转型。这就使得政府能够使用石油收入来支付慷慨的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如此慷慨,以至地主支持他们工人的罢工和对土地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自己也可以有资格被没收土地,并且以超过市场水平的价格获得补偿。实际上,沿着这一路线进行的改革可能对降低物质不平等程度的贡献非常有限。 [12]
补偿有时是通过秘密途径给予的。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过程中,古罗马共和国从被其击败的敌人手中没收了大量可耕种的土地,并且将它们转变为公共土地以分给定居者或者出租出去。后一种方式使得那些有实力对大片土地进行耕作和投资的人受益,从而公共土地更集中到富人的手中。在公元前133年做出对获得这类土地施加法律限制的早期尝试之后,事情发展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此时一个来自寡头统治阶级内部的民粹主义改革者提比略·格拉胡斯,实施了一项将每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限额设定为略多于300公顷公共土地的再分配方案。过量持有的土地被无偿征收,并且被分配给贫穷的市民。分配的这些土地不能转让,阻止了富有和有权势的人购买土地取代这些新发展而来的小地主。精英阶层对于这场改革的反对在持续。通过为定居者提供启动资金来促进这一项目实施的各种努力,最终驱使被激怒的寡头政治家夺走了格拉胡斯的性命。这一再分配方案在其发动者手中仅仅维持了不超过4年,到公元前2世纪初,租金已经被取消,同时所有公共土地的持有人,包括那些拥有最大允许数量土地的人,开始享有这种能被出售的私人土地产权。因此,尽管这一项目可能产生较大数量的新的小地主(数量与市民人口的一部分相当),其对于土地财富分配的较为长期的效应只可能是温和的。 [13]
在现代菲律宾,战争或者革命威胁的缺乏使得地主中的精英放缓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土地改革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竞选口号,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纵然在1988年,他们做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尝试,其结果依然是有限的,这和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情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尽管大多数的分成租佃式农民通过对多余土地的强制性出售获得一些土地,但由于对土地出售者存在偏袒和补偿性的要求,以及缺乏政府的支持,这一过程实际上提高了小地主之间的不平等程度。1848年夏威夷的《土地大分配法令》是产生不公平结果的和平性土地改革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当时,集体耕作的土地在国王、酋长和大众之间分享着。因为建立私有产权需要申请者正式提出申请——这是很多平民家庭无法做到的,以及因为《外国人土地所有权法》很快允许外来者获得土地,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没有被皇室申明产权的土地归入非夏威夷人的商业性所有权当中。 [14]
非暴力的土地改革只可能在一些最为罕见的情况下取得完全的成功。18世纪晚期,在西班牙发生的公共土地分配最多可以在部分意义上作为一个范例。在1766年发生的迫使查尔斯三世逃离马德里的暴乱触发下(因此也并非没有暴力的动因),出于本地的环境,这场土地改革产生了差异显著的结果。常常是那些能够支付农业生产工具的人可以从中受益。在某些区域,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资金,同时受到了精英阶层操控性的干预,改革遭遇了失败。只有当上层阶级没有特别地专注于土地所有权时(如在马拉加),商人精英在土地所有权上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当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和土地的相对匮乏限制了地主的议价能力时,如在瓜达拉哈拉一样,土地改革才会成功。 [15]
在19世纪的塞尔维亚,平等化的土地改革在其获得独立之后才成为可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塞尔维亚施加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与他们有着很好关系的穆斯林的封建制度。另外,强大的土耳其人压榨塞尔维亚农民,违法设立一种准私人性质的夺取产权的方式。本地农民被强迫支付较高的地租并提供劳务服务。1804年的起义之后,塞尔维亚迎来了双重统治的转型时期——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塞尔维亚自治从1815年持续到1830年,非法的产权主张被废除,同时封建地主和地租开始受到压制。1830年早期的一些方案要求大多数土耳其人在将其土地卖给本地人之后的几年内离开塞尔维亚。封建主义制度已经被废除,塞尔维亚人获得了土地上的私人权利。离开的土耳其人所放弃的一些土地被分配给了小农户。剩下的大地主被要求卖给耕种者一些房产,以及卖给在其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一定数量的农田。结果是,大地主几乎完全消失了,同时产权变得极为分散:到1990年,91.6%的塞尔维亚家庭拥有了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在这个例子当中,在以“外国”精英阶层被强迫放弃其传统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不平等程度得到降低。以之前的殖民者或者其他被掌控的精英资产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同样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 [16]
真正的和平改革常常需要某种形式的外国势力的控制,以限制本地精英的力量。这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波多黎各发挥了作用——即使在这里,也仅是大萧条和“二战”驱动下的美国平等化改革的一种副产品,它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发生的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恰好同时发生。殖民统治者在爱尔兰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作用。19世纪70年代晚期,鼓吹平等地租和保护佃农免遭驱逐的所谓“土地战争”,受到以罢工和抵制为主要形式的有组织的抵抗,但只有非常少的实际暴力行为发生。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应对这些怨言,这些法案管制了地租,并且为佃农提供固定利息的贷款,这些佃农希望从有出售意愿的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在1903年,《温德姆法案》在政府同意用国家收入支付佃农提供的补偿和地主的叫价之间12%的溢价的情况下换来和平,从而为小农场的私有化提供了补贴。这就使得小农场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独立的时候,控制了爱尔兰全国一半以上的农田。 [17]
寻求和平、有效的土地改革的努力并不是特别成功。最有再分配效应的干预也许是由革命和内战造成的,也常常是暴力的,就像在法国、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玻利维亚、古巴、柬埔寨、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大革命一样;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形式的暴力动荡,就像在津巴布韦一样。在其他一些例子当中,均等化的土地改革是国外占领的战争(日本、中欧,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朝鲜),战争的威胁(中世纪早期的日本、普鲁士),其他与战争相关的骚乱(危地马拉),对革命的担心(智利、秘鲁、埃及和斯里兰卡),或者是这些担忧和实际发生的战争(韩国和斯里兰卡)的一种组合所导致的。根据最新的调查,1900—2010年,超过87%的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外的主要的土地改革,都紧随着世界大战、非殖民地化、共产主义上台领导而产生。 [18]
如同在夏威夷和委内瑞拉一样,和平的改革可能使得富人受益,或者就像在爱尔兰和波多黎各一样得到公平的实施。关于和平开展并且导致重要矫正作用的自发土地革命的证据并不充足。这一结果并不让人奇怪:在那些迫切想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当中,精英阶层的抵制常常可以阻碍或者削弱再分配的政策,除非暴力性冲击或者暴力的威胁要求更多实质上的让步。这就有助于解释明显缺乏带有较高“地板”(新的小农场的规模)和较低“天花板”(地主所有权的上限)特征的非暴力性土地改革的原因。 [19]
如果我们进一步回望更为久远的过去,这种图景也不会变化。表面上雄心勃勃的土地再分配计划不断被证实具有建立政权的特征,如同战国和隋唐时期以及汉朝时的中国,具有统治者竭力压低精英阶层财富的背景,我已经在之前的一些章节中提到了这些观点。在古希腊,土地改革和一些作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债务免除通常都与暴力政变相联系。从古风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类记载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希普塞卢斯,作为柯林斯的第一个暴君,在消灭或者驱逐其反对派成员之后夺走他们的土地进行再分配。大约在相同时间或者稍晚一点,相邻的麦加拉城的忒阿根尼斯屠杀了富人在穷人土地上的牧群。在后来激进的民主时期,富人们被流放,其资产也被夺走,据说当时的穷人进入了这些富足的居所索取免费的食物或者实施暴力。虽然没有彻底取消债务的信号,不过借贷人被要求返还债务的利息。公元前280年,在奴隶和制造业工人的帮助下,阿波罗陀洛斯在卡桑德拉城掌权。据说他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并且在穷人当中进行再分割,同时提高了士兵的酬劳”,这种状态仅仅维持了4年。在相似的环境中,克里尔考斯在公元前364年成为赫拉克利亚–本都卡的君主,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土地再分配和取消债务的方案。 [20]
斯巴达的和平式土地改革也没有获得很多的进展。如同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土地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使得越来越大比例的公民被边缘化,全权公民的数量已经下降到700人(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数量是这一数字的10倍以上),其中100人被划分为富人阶级,其他人是他们的债务人。其他大约2000个斯巴达人被划分为二等公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已经下降到必要的阈值之下。公民群体中存在极端的不平等状况,更不必说斯巴达社会的其他下层阶级,这些情况为各种改革的尝试开辟了道路。
公元前3世纪40年代,由亚基斯四世实施的、意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的第一次干预,目标是取消债务,并且把土地分成大小相同的4500块,再分配给公民和从属城邦的部分成员。当他外出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些努力都遭遇了挫折,亚基斯本人被流放,改革也失败了。第二轮干预变得更加暴力,公元前227年,国王克利奥米尼斯三世在雇佣兵的帮助下通过政变上台之后,杀害了斯巴达5位资深执政官中的4人,以及大约10位其他官员,并驱逐了80多人。他的计划与亚基斯的类似,并且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同时伴随着很快取得军事和外交成功的军事改革。最终他的统治在公元前222年的战败后被推翻,克利奥米尼斯逃走了,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再分配措施被篡改了。然而,这场战败带来的大量伤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地主的数量。公元前207年,进一步的军事灾难促进了第三轮,也就是最激进的一轮改革,在纳比斯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奴隶”(也包括黑劳士)获得自由和解放。人们认为,他杀害、用酷刑折磨或者流放了富有的斯巴达人,并且将他们的土地分给了穷人。在他公元前188年被外国侵略者赶下台后,侵略者施行的一种反动的方案强迫将最近解放的黑劳士驱逐或者卖掉。这其实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实施倾向于借助某种暴力措施的另一种表现,同时它也表明,这反过来会释放更强烈的报复性暴力措施。 [21]
尽管我们可以说,没有与某种方式的暴力联系起来的土地改革,如果有的话,也很少成为对抗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有效方式。可能对于债务免除而言,也大体如此。债务当然是影响不平等状况的因素之一。债务问题迫使农民卖出他们的土地,吞噬其可支配收入。至少在理论上,减少或者取消债务可能会让富有的出借人付出代价、改善贫穷的借款人的状况。在实践中,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带来了真正的成效。有记载以来,最早的文明社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免除债务计划的证据:迈克尔·赫德森在取消利息或者债务本身,以及在公元前2400—前16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释放债务奴隶方面收集了超过两摞的证明材料,后者是一种在《圣经·旧约》的“利未记”中规定的,每五十年纪念一次的古代西亚地区传统。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皇家救济法令被认为是国家统治者和富有的精英阶层为控制盈余和征税及增兵能力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如果这种免除措施有效而且周期性进行,我们就能够期望这将会被计入贷款的条款(这可能会解释有记录的很高的利率);如果这有效但是很少见,或者常见但没有效果,那将不会对不平等状况起到什么效果。不管哪一种方式,都很难将免除债务视为矫正不平等状况的有效工具。 [22]
废除奴隶制看起来像是一种有希望的矫正力量。在那些相对较少的精英阶层的大量资本与奴隶捆绑在一起的社会,解放奴隶有压制财富不平等的潜力。然而,在实践中,大规模的废奴运动进程常常与暴力动乱纠缠在一起。在1792年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英国议会在1806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奴隶贸易的禁令,这是一项最初仅仅针对非英国殖民者的措施。其目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保护英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是军事利益。1823年在德梅拉拉发生的起义,以及1831年和1832年在牙买加发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促成了正式的废奴运动。《废奴法案》在1833年迅速颁布,迫使获得自由的奴隶为他们的前主人免费工作几年,并且为奴隶主提供补偿。此法案要求提供的2000万英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该国当时年度财政支出的40%,在今天价值23亿美元(或者如果用英国经济在当时和现在的一个比例来表示,实际上超过了1000亿美元现值)。尽管这要比这些奴隶的市场价值低——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时间段,其价值分别约为1500万、2400万,以及高达7000万英镑,考虑到4~6年没有报酬的学徒期,这种一次性的补偿方案的总价值不一定会带来显著的亏空。一半以上的费用流入地主和债权人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定居伦敦的商人和食利者。这些食利者中没人拒绝这种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矫正效应注定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在一个英国政府的收入要严重依赖关税和消费税这些间接税种的时期,承担大量债务来为这项计划融资的需求,实际上促使收入从大多数人手中被再分配给了更富裕的奴隶主和公共债务的购买者。 [23]
其他一些解放的例子甚至更直接地与暴力冲突联系在了一起。法国在1794年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一项把圣多米尼克(现在的海地)造反的奴隶拉回到自己一边,从而远离敌人的策略性手段。这一措施随后被拿破仑废除了。在1804年,当海地宣布独立的时候,此前的奴隶主被赶走,而那些滞留的人则在当年的白人大屠杀中丧命。需要另一场暴力冲击来终结剩下的法国殖民领地上的奴隶制度:1848年的革命,作为欧洲范围内动乱的一部分,再一次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制,并且导致奴隶被解放。奴隶主收到了一些现金和贷款的补偿,但是要比在英国得到的更少。战争促使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在殖民统治者臣服于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引发的本地起义之后,这些新成立的国家很快就通过了解放奴隶的法律。在第6章中,我讨论了美国内战对奴隶制度的暴力性摧毁,此时对于奴隶主资产的无偿征用被对非精英集团的间接破坏抵消,从而降低了整体上的矫正效果。同时,英国对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禁止,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暴力的行为,促进残留在拉丁美洲的奴隶制度的衰落。巴西和古巴是主要的壁垒。在古巴(以及波多黎各)的例子中,是暴力冲突再一次促进了政策的改变。1868年的古巴革命导致奴隶在一场持续了10年的战争当中得到解放。从1870年开始,改革限制了奴隶制,直到1886年古巴的奴隶制被废除。当巴西继续进口非洲奴隶,违反其外交承诺的时候,英国海军在1850年攻击了巴西港口并摧毁了运送奴隶的轮船,迫使该国禁止了奴隶贸易。只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不是主要由暴力驱动的:从1871年开始,其奴隶制度逐步瓦解,最终在1888年被废除,而且没有对奴隶主的补偿。 [24]
一般来说,不管是通过战争或者革命的方式,暴力牵涉得越多,矫正作用就可能更有效(如同在海地、拉丁美洲大部和美国)。反之,这一过程越为和平,将会带来更多的补偿,同时有能力的奴隶主能够更好地针对这一转型过程(如同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进行谈判。只有巴西的情况在部分意义上是一种例外。因此,不平等程度的降低通常与本书前面几章提到的暴力的矫正力量有关。相反,能显著实现平等化(在物质意义上)的和平解放是少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考虑到奴隶主通常控制着土地,并且能够从替代性的剥削性劳动安排中获得收益——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实施的分成租佃制,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应就更弱了。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经济衰退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第9章讨论的系统崩溃所导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具有我们能够从考古证据中识别出的矫正效应。紧随转型性革命而来的严重经济混乱可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虽然是在不那么剧烈的程度上。但是,“和平性”的宏观经济危机,即那些没有根植于猛烈冲击的经济衰退的作用是什么呢?对大部分人类历史而言,这些不平等程度的发展带来的危机所导致的结果是无法调查的。较早的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的持续性经济衰退,在此期间,随着羊毛出口、贸易和城市活动的减少,实际人均产出在整个17世纪的上半叶也降低了。不平等的结果也会随着我们选择不同的代理变量而存在差异:虽然地租与工资的比例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意味着劳动回报要比土地回报更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名义人均产出和名义工资之间的比率相当稳定,表明收入分配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也许在部分意义上是可得数据受到限制的结果,凸显出在前现代社会中探究经济力量引致的矫正效应的困难性。 [25]
只有更为晚近的事件才拥有大量的证据。主要的经济危机对不平等状况并没有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负面效应。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调查审视了1911—2010年间发生的7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和从其峰值下落了至少10%的100次消费衰退,以及1911—2006年间101次下降了同样程度的GDP下落。这些不同类型的事件仅在一般程度上存在重叠:例如,仅有18次银行危机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在25个国家发生的7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中,有37次产生了有用的信息。这些结果偏向于支持上升的不一致性:收入不平等程度仅仅在3个案例中下降,在7个案例中上升,如果人们将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可用的数据包含在内,这一数字就会上升到13。消费下降更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36个可用的例子当中,有7个案例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只有2个案例有了上升。至于GDP的收缩,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在这两种宏观经济危机当中,大多数例子只显示出非常小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一项单独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67次GDP衰退的研究当中,识别出10个这些事件导致不平等上升的例子,这显示出更贫穷的国家面对这种冲击时更为脆弱。我们必须得出宏观经济危机不能作为重要的矫正方式的结论,同时银行危机甚至倾向于有着相反的效果。 [26]
一项对1880—2000年间16个国家的调查证实了上面的最后一个发现,不过添加了一个时间维度。“一战”前和“二战”后的金融危机,倾向于通过更快地降低较低水平人群的收入(比起最高收入者),提高不平等程度。主要的例外就是大萧条时期,即使是最富有的、严重依赖资本收入的群体收入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也上升了。大萧条是美国唯一一次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强有力影响的宏观经济危机: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财富份额在1928—1932年间从51.4%下降到47%,正如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28年的19.6%下降到三年后的15.3%——如果将资本收入包含在内的话,则同一时期从23.9%下降到15.5%。最富有的0.01%的群体的损失特别的明显:他们包含资本收益的收入比例在1928—1932年间从5%降到2%。富有阶层的排名也相应缩水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会员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1933年间下降了2/3以上,银行的数量在1929—1933年间也从大约25000家下降到14000家。 [27]
总体而言,大萧条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全球效应更为温和。在澳大利亚,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28年的11.9%下降到1932年的9.3%,不过在1936—1939年之间的平均水平为10.6%,比危机之前的水平没有低多少。在法国轻微地恢复之前,这一数字从1928年的17.3%下降到1931年的14.6%。同时,在荷兰则是于1928—1932年间从18.6%下降到14.4%,此后也同样跟随着部分的反弹。在日本,这种下降趋势相应地比较微弱和短暂,在新西兰就更加弱了。在这些年份当中,德国、芬兰和南非的最高收入者的份额保持稳定,而在加拿大和丹麦发生了实际上升。大萧条的平等化结果因此看起来大体上局限于美国。不过即使在美国,它也产生了好坏参半的结果:在矫正效应出现几年之后,直到发生战争,收入的集中度都保持稳定,战争开始后,不同的财富不平等测度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 [28]
1929年10月29日、股票市场暴跌的4天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一场演说中有个著名的错误断言,即“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活动,即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还处在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之上”。但是,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基础可能要比其不久之后所表现的更为稳固:在20世纪30年代末,精英阶层收入和财富反弹的信号应该让我们感到怀疑,即如果其没有被再次爆发的世界大战夺走的话,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归根结底,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的恢复能力和反弹力,在最近的历史当中也是典型的。1987年的股票市场崩盘无法阻碍那一时期最高收入群体收入稳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适度的均等化效应以及下一年的“9·11”事件带来的混乱到2004年就完全消失了。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也是如此,其对于最高收入群体的负面效应在4年之后完全消失了。不管我们考虑的是美国顶层1%、0.1%还是0.01%的收入群体,结果都是如此。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平等化的效应是异质性的,但同样较为温和。经济危机可能是严重的冲击,但在没有暴力压力的情况下,国家通常并不能仅仅依靠其自身来降低不平等程度。 [29]
乍一看,民主制度的扩张看起来像是和平性矫正工具的合理候选人。然而,如同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看到的,正式的民主化不能轻易地被视为与暴力行动无关的自主发展。正如古代雅典民主制的演化似乎与动员群众的战争纠缠在一起,在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时段,选举权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普及显然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有关。仅仅是这个原因,即使民主化看上去对于这些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有一种平等化的效应,这种平等化效应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由战争的压力所驱动的。 [30]
此外,关于民主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模糊性,现在已经被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问题最有雄心和全面的调查证实了。基于对184个不同国家从独立或者1960年(或稍晚一些)开始,一直到2010年的538个观测样本的描绘,达龙·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民主对市场乃至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影响并不一致。民主对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许多基本的不平等测度不够精确,确实留下了可以被质疑的空间。然而,这种显著性关系的缺乏使得所有分析更为令人注目,原因在于民主对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确实有很强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民主在形成资源净分配时的作用是复杂且异质性的,民主与平等化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通常并不明显。原因有二:如果民主被有势力的选民“俘获”,平等化进程将会受到阻碍,同时民主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各种机会,但也可能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 [31]
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所做的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削弱了西方世界认为的民主化会约束物质不平等的观念。他们发现政党体制(政府是否由左翼政党控制)对于1916—2000年间13个国家的整体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什么影响,同时仅仅对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比例有着很小的抑制效果。集中的、国家层面的工资协商同样也没有带来较大影响。他们也研究了选举权的扩大与党派之争以及最高所得税之间的关系。因为最高所得税一般会与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并且常常比不平等程度本身有着更好的证据材料,它们应该可以在获得可信赖的不平等测度之前充当一个粗糙的代理变量。舍韦和斯塔萨维奇发现,男性普选权的引入对于最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并没有很强的影响:在15个国家当中,实施普遍男性投票权的前5年的平均最高税率只比接下来的10年稍微低一点。从1832年的《改革法案》到1918年男性普选权引入英国,选举权的扩大没有提高最高的税率水平。这些税率是被“一战”推高的,同时选举改革是追随而不是先于这一快速的剧变。最后,对转型为左翼政府之前和之后的平均最高所得税率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这5年间——这些事件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内——平均值仅增长了3个百分点(从48%上升到51%)。 [32]
相比之下,工会的力量实际上与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然而正像我在第5章中所展示的,工会化比例对于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非常敏感,因此它不能作为民主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函数或者表现形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经认为:“我们或者能够在这个国家拥有民主,或者能够让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能两者都拥有。”结果发现,我们实际上能够两者兼得,只要我们用正式的词汇来定义民主,而不是用更符合这一知名学者意图的、更宽泛的实质性观念来定义它。相反,强有力的民主政府的缺位也绝不意味着与经济平等不兼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保持早期暴力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成果上有着优良的记录,这些冲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主化运动聚集起能量之前,新加坡大体上也是如此。 [33]
[1] 思想,或者更确切的是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平等化收入和财富分配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毫无疑问,正像我们可能大体上定义为知识存量的一些其他要素,从各种宗教教义、废奴主义和社会民主,一直到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长期以来都深深地陷入各种矫正过程当中。这些意识形态不仅导致了暴力冲击,也有助于维持由此产生的平等化成果(最近的现代福利国家),进而也被这些冲击塑造并时而受到这种冲击的推动(参见本书第5章)。进一步地,规范化的思想倾向于在大体上与特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平等主义的信念在弱肉强食和现代高收入社会比在农业社会中更为普遍(Morris,2015)。同时,对于这一研究的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能否表明意识形态能够作为一种自治的以及和平性的矫正方式:它能否在暴力冲击的环境之外带来显著的经济平等化。现实常常并非如此:我后面讨论了一种可能的例外情形,即拉丁美洲近期的一些经济发展状况。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如果没有暴力性冲击,意识形态能否有机会发挥这样的作用,这实际上与我在第14章末考察的反事实情景有关。
[2] France and Britain: Piketty 2014: 116–117 figs.3.1–2.
[3] Moyo and Chambati 2013a: 2; Moyo 2013: 33–34, 42, 43 table 2.2; Sadomba 2013: 79–80,84–85, 88.For Mexico, cf.herein, chapter 8, pp.241–242.
[4] Powelson 1988: 176 (reforms); for the context, see Batten 1986; Farris 1993: 34–57; Kuehn 2014: 10–17.
[5] Leonard 2011: 2 (quote), 32–33; Tuma 1965: 74–81, 84–91; Leonard 2011: 52–58.
[6] Powelson 1988: 104–105, 109.
[7] Powelson 1988: 129–131 (Bulgaria); Barraclough 1999: 16–17 (Guatemala).
[8] You n.d.: 13, 15–16; Barraclough 1999: 34–35; You n.d.: 43 table 3; Lipton 2009: 286 table 7.2; You n.d.: 23; and see esp.You 2015: 68–75.Estimates for the 1960s vary from 0.2 to 0.55 but center on the 0.30s: 0.34, 0.38, or 0.39.For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security concerns and American influence in driving policy, see You 2015: 85–86.
[9] Romania: see Eidelberg 1974: 233 n.4 for references to this position, not shared by Eidelberg himself (234).Chile: Barraclough 1999: 20–28.See also Jarvis 1989 on the later unraveling of the reform’s redistributive effects, mostly via sales by smallholders.
[10] Peru: Barraclough 1999: 29–30; Albertus 2015: 190–224, who emphasizes the rif t between the ruling military and the landed elite.Even so, considering that the Peruvian land Gini was inordinately high to begin with (in the mid-0.9s), even robustly redistributive outcomes left it high, in the mid-0.8s: Lipton 2009: 280.Other countries: Lipton 2009: 275;Diskin 1989: 433; Haney and Haney 1989; Stringer 1989: 358, 380.El Salvador: Strasma 1989, esp.408–409, 414, 426.
[11] Quote from Al-Ahram on September 4, 1952, quoted by Tuma 1965: 152.Albertus 2015: 282–287 (Egypt); Lipton 2009: 294 (Iraq).Sri Lanka: Samaraweera 1982: 104–106.Since then, village expansion and regularization of encroachments have been the main mechanisms of adding land to smallholdings: World Bank 2008: 5–11.
[12] Lipton 2009: 285–286 table 7.2.Cf.also Thiesenheusen 1989a: 486–488.Albertus 2015:137–140 offers a more optimistic assessment regarding Latin America, where more than half of all farmland was subject to reform-related transfers between 1930 and 2008 (8–9),but it is telling that some the most successful redistributions occurred in Bolivia, Cuba, and Nicaragua alongside Chile, Mexico, and Peru (140).Venezuela: Barraclough 1999: 19–20.
[13] Roselaar 2010, esp.221–289.
[14] You 2015: 78–81 (Philippines); Lipton 2009: 284–294 (South Asia); Hooglund 1982: 72,89–91 (Iran).Increased inequality in landownership is not an uncommon outcome of land reform: see, e.g., Assuncão 2006: 23–24 for Brazil.
[15] Spain: Santiago-Caballero 2011: 92–93.In Guadalajara, its effect on inequality remained modest: 88–89.
[16] Zébitch 1917: 19–21, 33; Kršljanin 2016, esp.2–12.For other cases since 1900, see Albertus 2015:271–273 table 8.1.
[17] Barraclough 1999: 17 (Puerto Rico); Tuma 1965: 103 (Ireland).
[18] Survey: Albertus 2015: 271–273 table 8.1(31次“主要的”土地改革中的27次如此,其定义是,在一段至少一年的连续时间内,至少10%的可耕种土地所有者改变,而且其中超过1%是没收而来的土地)。For two of the other four—Egypt and Sri Lanka—see herein.Of all fifty-four land reforms, thirty-four, or 63 percent, in Albertus’s data se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Albertus himself stresse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coalitional splits between landed and political elites that made land reform possible,often under conditions of autocracy (esp.2015: 26–59).His finding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my own perspective.
[19] Lipton 2009: 130.For the reasons given herein, his examples—South Korea and Taiwan—do not qualify as genuinely nonviolent reforms.For problems with land reform implementation in general, see 127, 131–132, 145–146.Tuma 1965:179.从他对于土地改革的全球性观测中得到了这一结论:“危机越重大,传播范围越广,改革就会更势在必行、更激进和更有可能。”他也对在私有产权架构下进行,在范围上有限制,可能保持甚至提升不平等程度的改革,以及对那些通过集体化消灭私人占有,并且确实消除了财富集中的改革进行了区分。
[20] For China, see herein, chapter 2, pp.63–64, 69 and esp.chapter 6, pp.182–183.For all we can tell, the Solonic reforms in Athens did not involve actual land redistribution, and the nature of debt relief remains obscure.Moreover, they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foreign policy incentives: see herein, chapter 6, p.192.Link 1991: 56–57, 133, 139; Fuks 1984: 71, 19.
[21] Hodkinson 2000: 399; Cartledge and Spawforth 1989: 42–43, 45–47, 54, 57–58, 70, 78.The Greek data also mesh well with Albertus’s 2015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autocracy in implementing land reform.
[22] Hudson 1993: 8–9, 15–30, 46–47 (Mesopotamia); Leviticus 25, with Hudson 1993: 32–40,54–64.See also more generally Hudson and Van De Mieroop 2002.It is astonishing that Graeber 2011, in his global survey of debt, does not properly address this question.
[23] Draper 2010, esp.94–95, 106–107, 164, 201.
[24] Schmidt-Nowara 2010; 2011: 90–155 provides recent overviews.
[25] Á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13: 9, 18–21.See also herein, chapter 3, p.99 fig.3.3.
[26] Atkinson and Morelli 2011: 9–11, 35–42;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53.Atkinson and Morelli 2011: 42–48; Morelli and Atkinson 2015 find that rising inequality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outbreak of economic crises.
[27] Bordo and Meissner 2011: 11–14, 18–19 (periodization); Saez and Zucman 2016: Online Appendix table B1 (wealth shares; cf.previously Wolf f 1996: 436 table 1, with 440 fig.1);WWID (income shares); Turchin 2016a: 78 fig.4.1, 190.
[28] The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 and the overall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remained flat between 1932 and 1939: WWID; Smolensky and Plotnick 1993: 6 fig.2.Wolf f 1996: 436 table 1 observes a partial recovery in top wealth shares between 1933 and 1939 whereas Saez and Zucman 2016:Online Appendix table B1 document an ongoing reduction.
[29] For the Great Recession see Piketty and Saez 2013; Meyer and Sullivan 2013 (USA);Jenkins, Brandolini, Micklewright, and Nolan, eds.2013, esp.80 fig.2.19, 234–238 (Western countries up to 2009).See also Piketty 2014: 296.
[30] See herein, chapter 5, pp.167–169 and chapter 6, pp.192–194.
[31] Acemoglu, Naidu, Restrepo, and Robinson 2015: 1902–1909 (literature review), 1913–1917(data), 1918–1927 (effect on taxes), 1928–1935 (effect on inequality), 1954 (reasons for heterogeneity).The observed effect on disposable income Ginis is small—about 2 to 3 points (1928).Their findings expand on those of more limited earlier studies that likewise failed to identify a connec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al and welfare policies, such as Mulligan, Gil, and Sala-i-Martin 2004, and represent a departure from some of their own earlier arguments (e.g.,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see herein, chapter 13, pp.368–374.
[32] Partisanship and centralized bargaining: Scheve and Stasavage 2009: 218, 229–230, 233–239.Top income tax rates: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63–72, esp.figs.3.5–7.
[33] Unionization: see herein, chapter 5, pp.165–167.Asian countries: WWID.
到目前为止,我分析的这些过程几乎都没有为和平性的矫正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非暴力的土地改革、经济衰退和民主化可能偶尔起作用,但是对于不平等状况没有系统性的负面影响。显著平等化的土地改革或者奴隶的解放通常都明显和暴力活动相关,这种关联性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提供了进一步支持。低收入群体大规模地向国外迁移,有可能降低特定人群中的不平等程度:例如,有猜测认为,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在“一战”前的一代人时间内移民到新世界,在工业化不平衡的时期,这有助于稳定甚至可能降低意大利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群体占比。这种类型的转移起到了一种人口学上的矫正作用,这类似于第10章和第11章讨论的流行病的作用,但更为温和。然而,虽然移民可能是一种既和平又有效的平衡手段,但大规模发生时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至少对最小群体以外的人而言)这取决于非常特定且历史上罕见的情况。最为显著的是在19世纪中叶和“一战”期间,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较小程度上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结果可能相当复杂,这取决于移民群体相对于原籍人口的构成和汇款的作用。由于所需要的资源和很多东道国的政策,今天向外的移民常常来自社会当中境况较好或者受到良好教育的那部分群体。另外,如果没有考虑移民对于接收群体的不平等化效应,移民对不平等程度影响的任何评估都可能是不完整的。 [1]
这样,我们就只剩下有时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制力量:经济发展。乍一看,国家财富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毕竟,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其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前几代人的水平,而且与许多欠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它们往往表现得很好,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有石油蕴藏丰富国家的更可靠数据,例如那些波斯湾国家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得到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将外籍居民包含在内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因此需要通过排除那些严重依赖商品出口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来限定高人均GDP和温和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任何联系。但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与出现的问题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富裕西方经济体,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一般都是由20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暴力冲击,以及由此助推产生的政策和经济后果决定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尽管这些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而且通常并不是特别不平等,但后者不一定是由前者造成的。考虑到这些转型冲击的严重性和它们对整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讨论不平等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意义并不大。 [2]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从两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通过考察人均GDP本身与这些不平等测度有着系统性关联的主张,以及聚焦于没有牵涉从1914—1945年的(如果我们将亚洲的革命包含在内,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暴力性混乱的那部分地区。或者更确切地说,聚焦于那些没有像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直接牵涉其中的地区:非洲、中东,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
我们将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并受其驱动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归功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回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作为研究美国收入差距的先驱,提出了一个刻意简化的模型。如果城市中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也许收入分布得更不均衡,那么超越传统农业模式的经济进步最初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城市化也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例和城市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由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及整体上的不平等程度。一旦人口的大多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些差距将会缩小,这是一个对更为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城市工人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利做出响应,从而被工资水平的提高所强化的过程。这最后一个的因素,反过来又通过如税收、通货膨胀和对资本回报的控制等财政政策抑制富有阶层更高的储蓄率带来的不平等化效应。因此,按照库兹涅茨自己的话来说:
人们可能因此认为,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是长期收入结构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当从前工业化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是最为迅速的;然后暂时变得稳定;进而在后期一些阶段缩小了。
值得注意的是,库兹涅茨认为政治因素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于缴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发展:
(在财政措施和福利收益方面,)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必须强调长期波动的下行阶段,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长期过程中的扩大和缩小趋势发生了逆转。
然而在他的模型中,即使这些因素,也发生在经济变化之后,并且其预测在逻辑上取决于经济变化,基于这一原因:
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波动趋势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库兹涅茨自谦地将其这一贡献的特点描述为:
也许5%是根据经验数据信息得出的,同时95%来自推断,其中一些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污染”了……这种预感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一模型最终变得非常著名。它变得流行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像皮凯蒂在某种程度上敏锐地观察到的——它表面看起来是乐观的,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冷战’期间的好消息”,也是因为它似乎与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实证数据十分匹配,这些数据是库兹涅茨不可获得的。 [3]
跨国数据的集合将不同地方的人均GDP与不平等程度联系起来,表面上为库兹涅茨的预测结果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将其应用于全球数据集合,并且在一张图上描点后,通常会产生一条倒U形的曲线。低收入国家通常要比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更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更低(见图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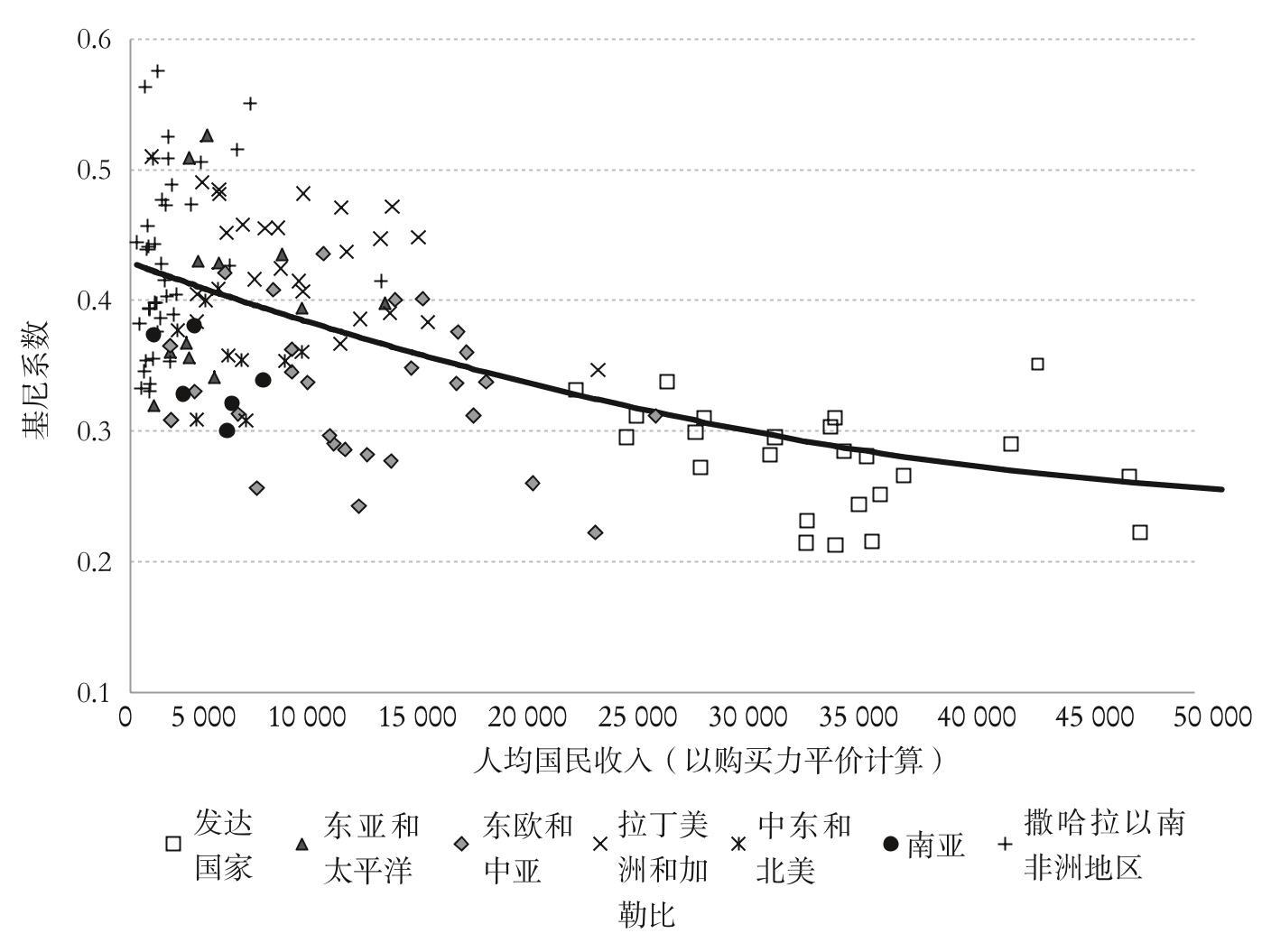
图13.1 不同国家2010年的人均同民收入和基尼系数
这种在不同国家产生的重要趋势已经被当作反映跨时变化的代理变量,以支撑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强烈的经济增长首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观点。因此,可以预测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理想类型经济体中,其不平等程度会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沿着这条倒U形的曲线发展。 [4]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多重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数据质量是我们的一项顾虑:利用世界不同地区的大量观测数据进行的调查,只有在它们能容忍有问题的精确度和可靠性的证据时才是可行的。可靠的结果要求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完全兼容的,但实际上常常并非如此。而且,更糟糕的是,跨国面板实际上越来越明显地被大规模的宏观区域特性破坏。因此,在这些面板数据中出现倒U形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两个不同地区,即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极高不平等程度造成的。根据一项在2005年前后进行的135个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调查,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处于最高位置。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中最富有10%群体的收入份额平均占41.8%,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均值为29.5%。如果排除拉丁美洲和一些高度不平等的南部非洲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或者用区域虚拟变量代替,倒U形曲线就在跨国样本的图中消失了。不管是基尼系数,或者是最高收入的十分位被用来衡量不平等程度,结果都将如此。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国家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到亚洲和东欧的中等收入国家,再到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现在一般都集中在0.35~0.45之间的收入基尼系数范围内。不存在系统性的取决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曲线。相对于人均GDP而言,不平等结果一般都相当具有异质性,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当中,具有较高不平等程度的美国和较低不平等程度的日本及部分欧洲国家并存。 [5]
因此,国家内部分析已经成为记录人均增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唯一可靠方式。一项1998年实施的纵向数据的开创性研究没有发现支撑库兹涅茨命题的证据。在分析的49个国家样本当中,有40个国家,在其经济随着时间推移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显著的人均GDP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在剩下的9个样本中,有4个国家的数据支持的是与倒U形分布相反的情况,这看起来颠覆了这一模型。49个国家中只有5个表现出显著的倒U形模式,尽管其中两个遇到了数据异常,为这一发现蒙上了疑云。这就使得我们仅剩下3个国家样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库兹涅茨式关系——其中一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相当小的国家(墨西哥和菲律宾是另外两个)。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调查的时间跨度可能太短因而不能产生更为可靠的观察结果,这些研究的发现也不能激发人们对库兹涅茨命题的更多信心。 [6]
其后,长期的国家内部调查没有为这种假设的关联提供太多实质性支撑。现在看来能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西班牙,1850—2000年,其收入的基尼系数先是上升,然后出现了下降。如果我们准备扣除20世纪40年代和第6章中分析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政权建立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剧烈短期波动,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长期性增长,即从19世纪60年代的大约为0.3的基尼系数值——此时的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用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增长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5的峰值,这时的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到1960年,整体水平下降到0.35左右,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从农业向工业逐渐转型的结果。反过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中总体上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整体上的倒U形曲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为2000美元的时候,同样没有达到不平等趋势的转折点:英国在1800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美国大约是在1850年,法国和德国则是在20年之后。同时,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在这些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也没有像1865—1907年间那样,明显地下降到更低的水平。 [7]
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聚焦的是农业人口的相对份额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库兹涅茨最初的两部门模型。预测的相关性再一次没有得到证据的证实:它没有在不同国家出现,同时在单个国家内部也不显著。最后,当我们用非参数回归方法比较多个国家内部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经济产出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规律联系。这种方法表明,即使在人均GDP的可比水平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趋势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总而言之,在识别倒U形模式和一些支撑性例子的持续性努力之外,大量的数据也无法为库兹涅茨60年前首次展望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的观念提供支撑。 [8]
经济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可预测的联系吗?答案取决于我们的参照系。我们必须考虑到存在多个库兹涅茨周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一些波动,其存在会干扰那些被设计用来寻找单一曲线的测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经济转型引发不平等现象应该少有质疑——不仅是从农业到工业系统,而且是从采集到农业模式,现在则是从一个工业化经济到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但是,矫正效应又如何呢?就像我在附录中提出的,有效的不平等(相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理论上的最大可能的收入集中程度)并不总是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传统的名义不平等衡量标准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在某些发展阶段,经济的进步预示着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主要的替代性选择与长期历史中的证据更为一致,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上升不大可能被逆转。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集中在所谓的“教育和科技之间的竞争”。技术变化决定了对特定技能的需求:如果供给滞后于需求,收入差距或者“技能溢价”会上升;如果供给赶上了需求或者过度增长,溢价则会下降。然而,这适用于一些重要的事项。这种关系主要适用于分析劳动收入,但不大可能影响资本的收益。在财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社会,这必然会削弱特定类型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总体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此外,在早期,除技能外,对劳动收入的限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奴役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或半依赖性劳动可能扭曲收入差距。 [9]
这样一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在前现代社会当中,为何技能溢价和不平等性没有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欧洲的部分地区,我们可以把时间回溯到14世纪。技能溢价的崩溃是对黑死病做出的反应,因为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我在第10章中分析了这一过程。在欧洲的中部和南部,一旦人口得以恢复,技能溢价就会再次上升,然而直到19世纪的末期,技能溢价在西欧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且是相当稳定的。后一个结果是不寻常的,部分原因似乎是熟练劳动力的灵活供给,还有部分原因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有助于维持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两者都受益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改善。然而,尽管中世纪末期技能溢价的下降伴随着一种普遍的收入不平等的矫正,但后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远远没那么直接:1400—1900年,西欧稳定的技能溢价并没有转变成稳定的不平等状态。 [10]
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发达,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就会更好,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技能溢价导致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我们必须问,控制技能供给的机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大规模教育是现代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受到国家间竞争驱动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一次性的暴力冲击是很敏感的。美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技能溢价的演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29年,手工行业中的技能比例要比其在1907年的水平低得多。不过,大部分的下降集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在我们拥有数据的5个职业中,22年时间里,有4个职业的净减少发生在1916—1920年间。在那个时候,“一战”提高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且重塑了体力劳动工资的分布。战时通货膨胀和冲突带来的移民流量的降低也促进了这一突然而强有力的均等化变动。白领和蓝领收入的比率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再一次地,1890—1940年间,整个净下降主要发生在19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这几年之间。 [11]
工资离差的第二次压缩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造成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新的强烈需求、通货膨胀和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这就导致所有男性工人中,顶层与底层群体的工资份额的比率不断缩小,同时降低了有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1939—1949年间,教育的回报率经历了戏剧性的下降,不管是受过9年教育的工人与高中毕业的工人相比,还是高中毕业的工人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相比,都是如此。尽管与战争相关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后来提高了这一均等化的压力,但即使是提高的大学入学水平也无法阻止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的部分性恢复。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急剧下降是仅有的存在记载的这种量级的变化。因此,即使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有助于限制以技能为基础的工资差距——它们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暴涨,但实际的矫正几乎完全限定在此国经受了战争引发的暴力冲击的相对短的时期内。 [12]
现在我要谈谈我的第二项策略,即通过在没有直接遭受过1914—1945年间的暴力冲击以及之后的余波,同时也没有经历过革命性转型的那些国家中寻找不平等程度减轻的例子,识别出经济的平等化力量。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这种方法以和平方式为矫正提供了少许坚实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没有出现长期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和瑞士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与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信息是冲突的。后苏维埃国家已经部分地从1989年或者1991年由贫困剧增导致的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上升中恢复过来。中国和印度这样非常大的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和越南,都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这4个国家一共占据世界人口的40%。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例如在泰国,抵消的情况是很少的。在中东地区,据报道,埃及在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这一数据的缺陷。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革导致不平等减弱后(本文第12章关于土地改革的一节对此进行了讨论),波动幅度不大,也许是这个国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他例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的伊朗,以及21世纪的土耳其。以色列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尽管市场收入不平等仍然相当稳定,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累退式再分配模式。 [13]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时被视为和平性的收入均等化的受益者。然而这种印象依据的是不可靠的基础:对所有28个可以获得这一时期的标准化收入基尼系数的国家而言,除了1个国家以外,基础数据都是匮乏的,同时不确定性的边界范围通常也很广。在南非这个有着高质量信息的单个例子当中,不平等程度依然相当平稳——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在其他27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观察不到显著的趋势,同时在另外5个国家当中,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升了。28个国家中仅有10个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它们仅仅占到总样本人口的1/5。更重要的是,相关基尼系数的置信区间往往很宽:在95%的置信水平上,它们平均在12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9~13个点之间(这一均值对不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大体上是相同的)。在许多例子当中,这些变化幅度超过了不平等程度隐含的变化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一个整体的趋势。然而,即使我们准备按照其表面上的数据接受这些结果,它们也将不会指向一个不平等程度降低的持续性过程。尽管该区域中的一些国家近年来能够很好地享受一种和平性矫正力量,这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能在此之上做出关于这种发展的本质、外延和可持续性的更一般结论。 [14]
给我们留下最大和最好记录材料的例子的就是拉丁美洲。在我们拥有数据的区域中,大多数国家从21世纪以来都表现出收入差距的显著降低。更为细致地思考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有道理的。根据此前几章中讨论过的暴力性矫正力量,这整个地区为我们提供了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与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最为接近的——尽管在很多方面不是特别接近的反事实。作为最罕见的一些例外情况,即拉丁美洲没有受到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这样强烈的暴力冲击的影响,它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温和的环境中探索不平等状况的演化。 [15]
一系列的代理变量数据和创造性的现代复原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可靠的收入基尼系数数据通常只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能得到,那时一些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数据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不能完全信任更早一些时期的研究发现。即使如此,追踪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过程已经变得可行了,至少在大体上是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保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是由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到正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所驱动的。事实证明,这一进程对精英阶层的益处过大,并加剧了不平等程度。 [16]
出口驱动的发展,在“一战”之后首次放缓,“一战”抑制了欧洲人的需求,并且当大萧条在1929年袭击美国的时候,它就陷入了停顿状态。“二战”进一步减少了至少部分形式的贸易活动。1914—1945年间的这些年份,表现为一个转型和增长减速的时期。在6个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持续上升,经过人口加权之后,基尼系数从1913年的0.377上升到1938年的0.428。尽管避免了被直接牵涉进这些战争当中,拉丁美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在区域外发生的暴力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之下。贸易中断和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流入是最重要的后果。这些冲击预示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经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同时向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转变。 [1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通过更为强烈地促进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的工业能力适应了这一全球趋势,并且通过依靠保护主义的措施来促进这种发展。这最终恢复了经济增长,并且在收入分配方面留下了烙印。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这些结果的差别很大。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提升了中产阶级、城市部门,以及白领工人在有工资的劳动力中的比例。这些变化有时伴随着更具福利导向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并且被其强化了。外部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1942年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和其他一些西方战后计划项目,都启发了南美洲南部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平等程度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影响。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时被弱化,例如在阿根廷,也可能会在智利;有时它们增长了,最明显的是巴西;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首先上升,然后下降了,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这些地方,非熟练劳动力的巨大存量和对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提高了不平等程度,直到这些压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消退为止。 [18]
尽管文献中普遍地提到了我们在向更大程度的收入平等化迈进,但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展示了一个不同的情况,特别当我们关注的是更长时间内的净结果时更是如此。在我们有数据的、可以回溯到1938年的6个国家当中,除了1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那一年到1970年之间都上升了,同时人口加权的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0.464变成0.548。在一个有15个国家的更大样本中,其中13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50—1970年间上升了,整体样本中的增长更为温和地从0.506变成0.535——以国际标准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经历了不平等程度净下降的3个国家当中,有2个国家的这种改善实际上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它们与胡安·庇隆激进的中央集权和再分配性政府相吻合;在危地马拉,它们发生在一场血腥的内战期间及之后。委内瑞拉因此成为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性矫正的主要候选国,如果我们接受另一组不平等状况估计——这些估计表明1930—1970年间的矫正是由经济及(和平的)政治变革推动的,那么智利可能也会加入这一行列。 [19]
20世纪70年代,用以维持保护主义政策和国有化产业的公共借贷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失落的年代”,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困扩大了。这反过来刺激了经济自由化,从而开放了区域经济并促使它们融入全球市场。在不同的国家中,不平等的后果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整个地区表现出来的是,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有温和的增长,每10年的提高要略微小于2个百分点,并且在2002年前后达到了峰值。 [20]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种经济条件下都提高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制度、经济停滞和自由化。在4个有着最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中,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348一路上升到1990年的0.552;有6个国家从1913年的0.377变为1990年的0.548;有15个国家从1950年的0.506上升到1990年的0.537。尽管这样的结果掩盖了局部的变化,并且平缓了暂时的波动,尽管准确的数值常常不为人所知,这种长期的趋势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至于能够发现的进步,它仅仅是20世纪下半叶不平等程度上升过程中的一个轻微的减速。正如我们在图13.2中能看到的,临时的矫正效果是短暂的,同时仅限于经济下行的那些时期,这是由20世纪第一个10年和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在英国、美国的宏观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国内和国际因素导致的深度衰退所触发的。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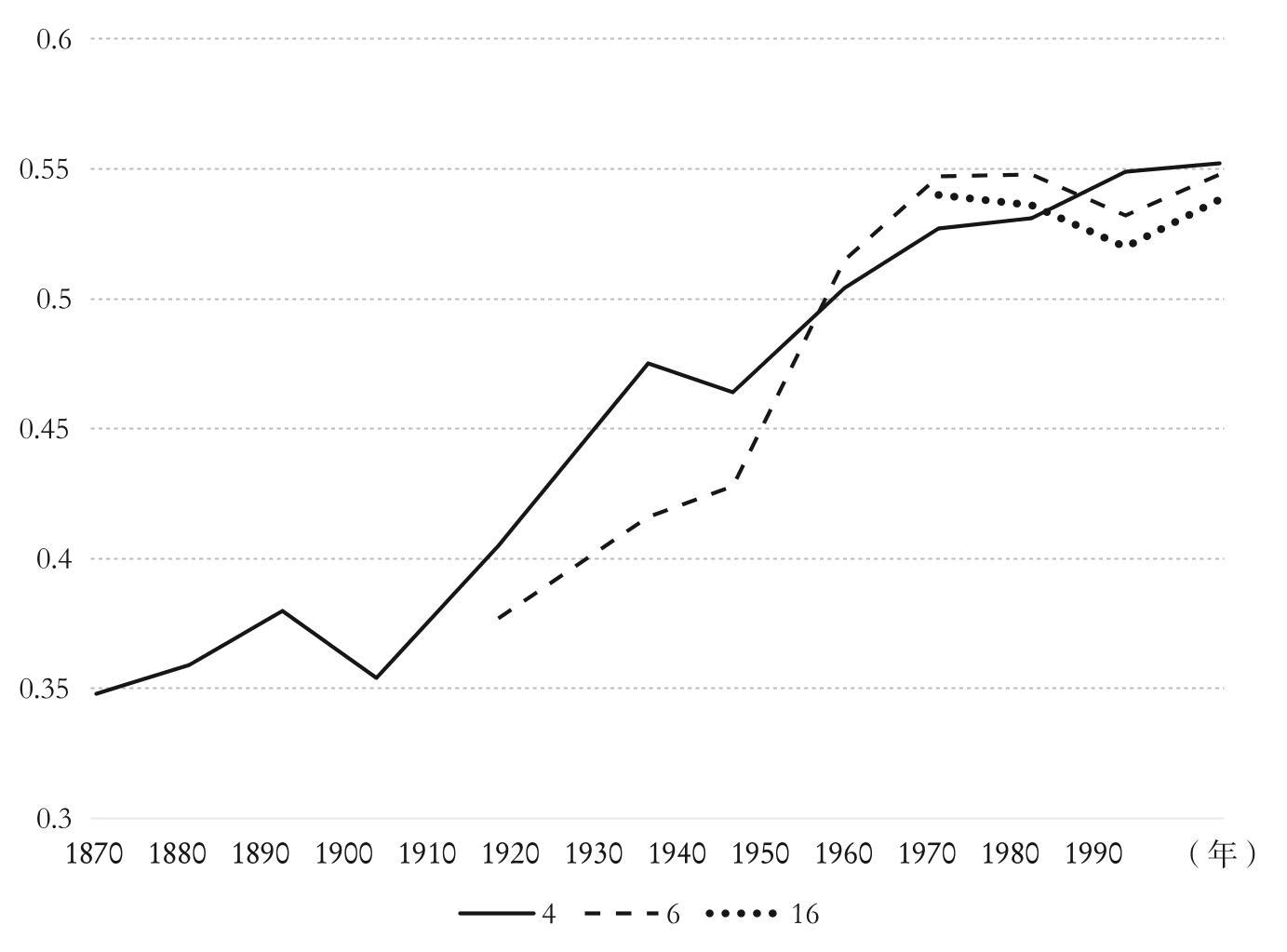
图13.2 对拉丁美洲收入基尼系数的估算和推测:1870—1990年(分别对4、6、16个国家人口加权的平均值)
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演化过程的最新阶段开始于2000年之后不久。这也许是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整个地区都下降了。在所有已经产生了相关数据系列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在2010年的收入基尼系数要低于它们在2000年的水平。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或许还有危地马拉,成为仅有的有记录的例外。对其他14个国家而言,市场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51下降到0.457,同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49下降到0.439,或者说每种测度的下降都超过5个点。这种收缩从其规模和地理范围上而言都肯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需要我们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它使得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从印度这个典型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水平降低到更接近于美国的水平,然而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得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从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水平提高到比美国这种西方国家中没有争议的“不平等冠军”依然高7个点的水平。因此,不要高估这些变化对于拉丁美洲收入异常失衡的分配的影响。 [22]
更为糟糕的是,从2010年开始,这种下行趋势在略少于一半的、我们有数据的国家中持续存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在那些年份里,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和秘鲁的不平等程度都相当稳定,墨西哥和巴拉圭则开始攀升,或许在洪都拉斯也是如此,只不过缺乏这里的证据。哥斯达黎加总是与整个区域的趋势背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不平等程度一直都有轻微的上升。所有这些对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所发生的矫正的原因和可持续性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这会不会是一种短暂的进步呢?
一旦这个区域中的国家已经越过了某种类型的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即此时这些经济体已经变得足够富裕,从而收入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那么几乎不可能将这种矫正解释为它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库兹涅茨式向下压力的结果。在2000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14个国家中,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均GDP相差7.6倍。虽然偏向较低的一端,这一较宽范围的离差还是非常整齐的:有5个国家的每年人均GDP的均值在1000~2000美元之间,有另外5个国家在2000~4000美元间,其他4个国家则介于5000~8000美元之间。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排除在接下来的年代中观察到的同步矫正是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正式的检验已经证实,尽管这些年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模型也不能解释大部分我们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23]
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几个原因: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和强劲的国外需求,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压缩;从先前加剧贫困水平的非平等化宏观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由更迅速的经济增长驱动强劲劳动力市场;以及某些政府转移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效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特别有希望成为长期维持平等化的一个潜在的和平性动力。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往往伴随着教育系统的扩张,这种扩张一直在持续,同时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供给,这反过来降低了更高层次教育和技能溢价的回报,也因此降低了整体的劳动收入不平等性。技能溢价的降低更多地归因于供给的改善还是需求的下降,这个问题并没有单一的答案。在一些国家,溢价缩小是对更弱的需求的反应,例如在阿根廷,这就为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布下了疑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因为有着中等或者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人的实际(而不仅是相对的)收入面对更弱的需求下降了。萨尔瓦多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的例子:对所有工人来说,实际工资都下降了,但受到更多教育的工人下降得更多。这就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平等化的结果并不总是来自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 [24]
在某些情况下,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产生的分配收益可能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根据一项惊人的发现,现在玻利维亚的教育价值如此之低,以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与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工人相比,工资溢价为零。这就指出了技能溢价降低的一个替代性或者至少是补充性的原因。随着接受超过基本水平的教育机会的增加,教育的质量可能已经恶化了,同时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可能很差。这种悲观的观点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秘鲁和智利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中学教育与雇主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后果产生了负面效应。 [25]
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可能是更为短暂的。国际上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缩小了农村工人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效果已经弱化了。2002年以来的一些平等化倾向,仅仅代表了之前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暴涨的一种恢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根廷,1998—2002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使得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从那时起,稳定的经济复苏,以及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移,降低了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压低了技能溢价,使得不那么富裕的一半人口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因此,阿根廷也拥有了更强大的工会和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同样在相似的恢复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不平等程度的缓解。根据一项估计,如果我们排除从危机中恢复而产生的平等化效应,2000—2005年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平均下降,其变化大约都表现在基尼系数的小数点后一位上,因此是非常温和的。更普遍的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带来的不利短期效果的减少发挥了一种缓和的作用。每年平均4%的经济增长,换言之是此前一些年代实际值两倍的强劲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但据估计这仅占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变化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有利的条件不再适用,因为这一区域的年GDP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的5年都在下降,从2010年的6%变为2015年预估的0.9%。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巴西——目前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据说将经受住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进一步矫正的前景。 [26]
最后,作为一种消除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工具,政府转移支付的扩张吸引了相当多的公众关注。例如在巴西,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转移支付的规模、覆盖面和分布的变化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家庭补助”计划已经触及1100万贫困家庭。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拉丁美洲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实际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事实上,大量贫困家庭的存在,使得即便是相对不多的转移支付(大约为GDP百分点的十分之几)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可能带来平等化效应。然而,西欧国家的总收入往往与可支配收入差别很大,而在拉丁美洲,它们则基本上不会这样。人们已经为此找了多种原因。以国际标准看,拉丁美洲征税的数量相对于GDP而言比较小,同时收入税特别低。同时,逃税现象也非常普遍,部分是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部分是由于存在规模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对于整个区域而言,平均的收入税免税额大约是人均GDP的两倍,在一些国家,累进税率只适用于很高的收入水平。政府收入的缺乏因此严重限制了转移支付的潜力。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福利计划反而有助于产生净不平等。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不成比例地有利于那些在收入分布的前20%的群体——他们主要是有着正规就业安排的城市工人,同时歧视农村人口和在非正式部门的人。只有一些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不同,因为它们大多支持的是在收入分布的下半部分的人群——但是它们也只是在不受收入限制和更多倒退形式的福利抵销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 [27]
为什么拉丁美洲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如此脆弱?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即暴力冲击的革命性力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的累进制财政系统牢牢根植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这种经济发展并不是衡量财政再分配程度的有效指标。1950年,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正忙于对富人征税和建立雄心勃勃的福利体系的时候,在德国、法国、荷兰、瑞典、英国和加拿大,人均GDP(1990年的国际美元标准)的范围是4000~7000美元,在日本是接近2000美元。那个时候,即使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也没有大幅度高出西欧国家。这些数值在那个时候,大体上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样领先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是一致的,与今天更大范围的拉丁美洲国家相同:在这一区域的8个最发达的主要国家中,等价的人均GDP在2010年是7800美元,在一个更大的样本中平均为68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比1950年的美国平均水平更好一些。 [28]
这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约束并不是由其经济表现决定的。在全世界,不仅仅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千百年来,暴力冲击已经成为财政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血腥的跨国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中只起到了非常小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多么严重。本区域所特有的许多特征都被援引来解释这一现象,尤其是种族主义、强迫劳工和奴隶的殖民制度的遗毒,以及庇护主义和寡头势力的持续存在。然而,我们试图使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规模持续存在合理化差异时,没有出现的那些因素可能是同等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先不说其合理性,收入平等化的重大突破的可行性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29]
与教育、外国投资、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公共支出有关的政策,大体上解释了21世纪以来在拉丁美洲发生的矫正效应。更纯粹的经济因素以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从之前的危机中恢复的形式为平等化做出了贡献,但已经被证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更为短暂的。随着经济复苏和外部需求的下降,进一步的矫正将要求更为激进的财政调整,以促进教育(考虑到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如果它源自不断下降的需求或糟糕的教育结果,那它就是好坏参半的)和扩张再分配性的转移支付。这一始于10多年前的矫正是否将会持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案例中是重新开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从现在开始的5~10年里,我们将对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30]
我的结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只为和平的不平等程度的弱化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同时,至少在现在,缺乏暴力冲击就绝没有持续和实质性的矫正效应。在过去的150年中,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各种阶段都伴随着一些偶发的反转,这些反转与例如西方宏观经济危机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与在一些例子中激进的或者暴力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尽管很难不赞同玻利维亚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的格言,即“如果你将智力和职业能力与社会良知结合在一起,你就能改变一切”,拉丁美洲的历史对暴力方式在矫正不平等问题上居首要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反驳能力。 [31]
此外,本章和前一章分析的这些力量当中,没有一种对于物质不平等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和平的土地和债务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和经济增长都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时而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时而不能:简而言之,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当现代经济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于物质资本上升,同时当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供给的一个函数的时候,关系到后者的平等化政策可能看起来特别有价值。即便如此,尽管由于教育在工资差异上的影响,对教育上的投资可能确实是一种可行的非暴力矫正机制,但在历史上它一直被卷入不那么和平的进程:20世纪当中,关于美国技能溢价有记载的大幅波动再次显示了战争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经济回报中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工会化也是如此。再分配性的财政和福利政策确实减少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它们的规模和结构也往往与暴力冲击及其长期影响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西方和东亚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另一方面是拉丁美洲的状况,提醒我们要注意这种基本的联系。即使在评价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替代性原因之后,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不管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潜在的暴力,长期以来都是平等化政策措施的关键催化剂。
[1] Ginis for Italy: Rossi, Toniolo, and Vecchi 2001: 916 table 6 (decline since 1881); Brandolini and Vecchi 2011: 39 fig.8 (stability between 1871 and 1911).Italian emigration: Rossi,Toniolo, and Vecchi 2001: 918–919, 922.Positive selection among emigrants: Grogger and Hanson 2011.Mexico has been a partial exception: Campos-Vazquez and Sobarzo 2012:3–7, and esp.McKenzie and Rapoport 2007 for the complexity of outcomes.Remittances tend to reduce inequality but only to a small extent: see, e.g., Acosta, Calderon, Fajnzylber, and Lopez 2008 for Latin America.Immigration lowered U.S.real wages between 1870 and 1914: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180–181.Card 2009估计认为,移民为美国在1980—2000年间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贡献了5%。纵观历史,移民偶尔会从零开始创造出相当平等主义的定居者社会:这些例子的范围从古希腊的殖民者一直到美洲大陆的开拓者。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土著群体和新来者群体间不平等程度的相应增加,情况就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
[2] Alvaredo and Piketty 2014: 2, 6–7对产油国当前证据的缺乏进行了评论,注意皮凯蒂的观点,即“二战”后几十年中的强劲经济增长与不断下降的不平等有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1914—1945年间的暴力冲击,以及它们的政策后果导致了资本的回报率(去除税收和战时损失之后)下降到低于增长率的水平:Piketty 2014: 356 fig.10.10。
[3] Kuznets 1955: 7–9, 12–18, with quotes from 18, 19, 20, 26.Piketty 2014: 11–15 (quote: 13).
[4] Fig.13.1 reproduced from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18 fig.9.4, the most recent and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available to me.根据两位批评者对这一方法的一种恰当的特征描述,“从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国家得到的观察结果正被用来估计单一国家收入的演化”(Deininger和Squire 1998:276)。
[5] Data quality: Bergh and Nilsson 2010: 492 and n.9.Palma 2011: 90 fig.1 (Gini distribution),92 and fig.3 (top deciles), 93–109, esp.95 fig.5, 96, 99 fig.7 (inequality/per capita GDP relationship).The powerful pull effect of Latin America was already noted by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27–28.For Latin American “excess inequality,” see, e.g., Gasparini and Lustig 2011: 693-694; Gasparini, Cruces, and Tornarolli 2011: 179–181.此外,Frazer 2006:1467指出,跨国面板当中倒U形曲线较低不平等性的左尾分布,可能可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不平等、低收入国家数据的相对缺乏,这使得其他的低不平等、低收入国家,即一个贡献了更多观测值并且在人均GDP测度的较低一段压低不平等程度的群体,变得更为特殊了。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20 note further problems:隐含的1800美元的转折点是非常低的,同时,考虑到富国拉低了曲线的右尾,如果只考虑发展中国家,那么不平等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微弱了。在样本的几乎一半的国家当中,研究者“找不到任何不平等模式的类型和不同的发展及增长测度之间的显著关联”。
[6]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261, 274–282, esp.279.
[7] Here I diverge from the argument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what he calls “Kuznets waves”or “cycles” presented in Milanovic 2016: 50–59, 70–91.For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 shocks of 1914–1945, and for longer-term evidence for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 herein, chapter 3, pp.103–111 and chapter 5, pp.130–141.For Spain,see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8: 298 fig.3, 300; see Maddison project for GDP figures.It is striking that the Gini closely tracks per capita GDP, which declined after the Civil War: 300 fig.5.For civil war effects, see herein, chapter 6, pp.204–206.See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08 for work rejecting earlier findings concerning a Kuznets curve in Sweden since 1870.They also stress that because it was primarily a capital income phenomenon, the great leveling of 1914 to 1945 cannot be explained in Kuznetian terms (551).Milanovic 2016: 88 table 2.2 lists levels of per capita GDP ranging from $1,500 to $4,800 in 1990 International Dolla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national inequality peaks (expressed by Gini coefficients),but his survey remains problematic for several reasons.The suggested inequality peaks for the Netherlands in 1732, Italy in 1861,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1867 may not be genuine or directly comparable to later values.As for the Netherlands, only if we are prepared to put the conjectural Ginis for 1561, 1732, and 1808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somewhat lower value for 1914 is it possible to posit a pre-1914 decline, which was in any case followed by a much stronger and better documented subsequent reduction (81 fig.2.15).The notion of an Italian inequality peak in 1861 depends on Brandolini and Vecchi 2011:39 fig.8, who show very similar Ginis of around 0.5 for both 1861 and 1901 and identical lower ones for 1871 and 1921; their estimates generally fluctuate between 0.45 and 0.5 for the whole period from 1861 to 1931,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identify a meaningful turning point.For British inequality, see herein, chapter 3, pp.104–105.Leveling that commenced after Gini maxim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and Japan in 1937 is causally related to World War II rather th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 se.This leaves only the case of Spain referenced in the main text.There is no sign of GDP-related equ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see herein, p.383.
[8] Agricultural share: Angeles 2010: 473.While this does not disprove a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per se and inequality, it rejects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of the model and in so doing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findings that undermine it.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275–276 already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intersectoral movement is trivial to inequality outcomes, whereas interoccupational inequality matters most.Comparisons:Frazer 2006, esp.1465 fig.5, 1466 fig.6, 1477–1478.Continuing efforts: the most noteworthy recent attempt is Mollick 2012, on top income sha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9–2002 (see herein, p.413).Abdullah, Doucouliagos, and Manning 2015 argue for a link between rising inequality and per capita GDP in Southeast Asia and maintain that the required inflection point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no evidence for a Kuznetian downturn.Like Angeles 2010, they also fail to find the predi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s.
[9] “种族”的概念是廷伯根于1974年创造的。
[10] Premodern skill premiums: van Zanden 2009, esp.126–131, 141–143.For rising inequality after about 1500, see herein, chapter 3, pp.91–101.
[11] Goldin and Katz 2008: 57–88 analyze the long run of American skill premiums since the 1890s.For the first decline, see esp.60 fig.2.7 (manual trades), 63 (immigration), 65 (World War I), 67 fig.2.8 (white/blue collar earnings).
[12] Goldin and Margo 1992 is the foundational study of the “Great Compression” of wages related to World War II.Returns to education: Goldin and Katz 2008: 54 fig.2.6, 84–85 table 2.7 and fig.2.9; Kaboski 2005: fig.1.GI Bill and recovery: Goldin and Margo 1992:31–32; Goldin and Katz 2008: 83.Cf.Stanley 2003: 673 on the limited impact of the GI Bill.
[13] See SWIID; WWID.Developments in Indonesia have been more complex.For Western countries, see herein, chapter 15, pp.405–409; for postcommunist inequality, see herein,chapter 7, pp.222, 227 and chapter 8, p.254.For Egypt, see esp.Verme et al.2014: 2–3,and cf.also Alvaredo and Piketty 2014.Seker and Jenkins 2015 conclude that rapid poverty decline in Turkey between 2003 and 2008 was driven by strong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equalizing distributional factors.
[14] Recent inequality decline: Tsounta and Osueke 2014: 6, 8.Twenty-eight countries: SWIID for Angola, Burkina Faso, Burundi, Cameroon,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omoros, Cote d’Ivoire, Ethiopia, Ghana, Guinea, Kenya, Madagascar, Mali, Mozambique, Namibia,Niger, Nigeria, Rwanda, Senegal, Seychelles, Sierra Leone, South Africa, Swaziland,Tanzania, Uganda, Zambia, Zimbabwe.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35–736 also comment on the poor data quality.Ten countries with falls in inequality: Angola,Burkina Faso, Burundi, Cameroon, Cote d’Ivoire, Mali, Namibia, Niger, Sierra Leone,and Zimbabwe.This includes dubious cases—most notably that of a supposed decline in Angola, a notoriously unequal society.A strong drop observed in Zimbabwe may be related to political violence (see herein, chapter 12, p.347).
[15] 例外包括1864—1870年间极端血腥的巴拉圭战争,以及持续到1959年的古巴革命。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墨西哥,以及1978年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在范围和追求上都有更多的限制。即使是部分国家的失败,如2010年的海地,同样也是罕见的。事实上,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至于将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反事实的局限性例子,参见本章和第14章。
[16] Williamson 2009 (now also in Williamson 2015: 13–23) is the boldest attempt at long-term conjecture; see also Dobado González and García Montero 2010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Arroyo Abad 2013 (nineteenth century); Prados le la Escosura 2007(inequality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Frankema 2012 (wage inequality acros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lso Rodríguez Weber 2015 (Chile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First globalization phase: Thorp 1998: 47–95;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81–137.Inequality rise: Bértola, Castelnuovo, Rodríguez, and Willebald 2009; Williamson 2015:19–21.
[17] After 1914: Thorp 1998: 97–125, esp.99–107 on international shocks;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138–147, 153–155.See Haber 2006: 562–569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ready in this period.Ginis: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7 table 12.1.
[18] Thorp 1998: 127–199;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138–197, esp.193–197; Frankema 2012:51, 53 on wage compression.Ginis: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7 table 12.1; but for conflicting data on Chile, compare Rodríguez Weber 2015: 8 fig.2.
[19] 1938–1970: Argentina, Brazil, Chile, Colombia, Mexico, and Uruguay, with a net drop in Argentina.1950–1970: the same countries plus Costa Rica, the Dominican Republic, El Salvador, Guatemala, Honduras, Panama, Peru, and Venezuela, with net drops limited to Guatemala and Venezuela.See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7 table 12.1.The Gini outcom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ovement of top income shares in Argentina, according to WWID.For Perón’s policies (such as price controls, minimum wages, transfers,unionization, labor rights, and pension system), see Alvaredo 2010a: 272–276, 284.For Chile, see the previous note.
[20] Thorp 1998: 201–273; Haber 2006: 582–583;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199–257.Rising inequality: 253 (growing wage gaps).Heterogeneity: Gasparini, Cruces, and Tornarolli 2011: 155–156, and see also Psacharopoulos et al.1995 for the 1980s.Ginis: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7 fig.12.1 (1980/90); Gasparini, Cruces, and Tornarolli 2011: 152 table 2(1990s/2000s); Gasparini and Lustig 2011: 696 fig.27.4 (1980/2008).
[21] Fig.13.2 from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296–297 table 12.1.
[22] Data from SWIID.For a similar statistic, see Cornia 2014c: 5 fig.1.1 (a drop from 0.541 in 2002 to 0.486 in 2010).Palma 2011: 91 notes that between 1985 and 2005, Brazil’s global income Gini ranking fell from being the fourth-highest (i.e., fourth-worst) in 1985 to being the sixth-highest in 2005, a very modest improvement in relative terms.
[23] GDP: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 .PCAP.CD.Test: Tsounta and Osueke 2014: 18.
[24] Education and skill premiums: e.g., Lustig, Lopez-Calva, and Ortiz-Juarez 2012: 7–8 (Brazil),9–10 (Mexico);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31 (general).Central America: Gindling and Trejos 2013: 12, 16.
[25] Bolivia: Aristázabal-Ramírez, Canavire-Bacarezza, and Jetter 2015: 17.For the importance of falling skill premiums (rather than transfers) for Bolivian leveling, see Hernani-Limarino and Eid 2013.The observed lack of return casts doubt on the notion that increased education has been beneficial (Fortun Vargas 2012).Education quality: Cornia 2014c: 19;Lustig, Lopez-Calva, and Ortiz-Juarez 2014: 11–12, with references.
[26] Commodities: se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2015 for the drastic downturn in foreign demand in recent years.Argentina: Weisbrot,Ray, Montecino, and Kozameh 2011; Lustig, Lopez-Calva, and Ortiz-Juarez 2012: 3–6;Roxana 2014.Other recoveries: Gasparini, Cruces, and Tornarolli 2011: 167–170.One Gini point: 170.Abatement: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49.Effect of GDP growth: Tsounta and Osueke 2014: 4, 17–18 (maybe an eighth of the overall inequality decline).GDP growth rates: IMF data in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3/whd/eng/pdf/wreo1013 .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5/CAR042915A.htm.Cornia 2014b: 44 identifies several structural obstacles to further leveling.
[27] Brazil: Gasparini and Lustig 2011: 705-706; Lustig, Lopez-Calva, and Ortiz-Juarez 2012:7–8.Taxes: Goñi, López, and Servén 2008, esp.7 fig.2, 10–14, 18–21; cf.also De Ferranti,Perry, Ferreira, and Walton 2004: 11–12.Low transfers and regressive benefits: 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254–255; Medeiros and Ferreira de Souza 2013.For low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e generally, see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50, who also explain them with reference to low levels of taxation; and see also Besley and Persson 2014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asons for low taxation levels.
[28] GDP measures: Maddison project.
[29] Violent shocks and fiscal expansions across world history: Yun-Casalilla and O’Brien 2012;Monson and Scheidel, eds.2015.Minor role: herein, p.378.Features: De Ferranti, Perry, Ferreira, and Walton 2004: 5–6 briefly summarize the conventional view, qualified by, e.g.,Arroyo Abad 2013; Williamson 2015.Palma 2011: 109–120 emphasizes the resilience and success of Latin American oligarchies in maintaining high income shares.Williamson 2015:23–25 observes that Latin America missed out on the “Great 20th Century Egalitarian Leveling.”
[30] Main causes: Cornia 2014c: 14–15, 17–18; Lustig, Lopez-Calva, and Ortiz-Juarez 2014: 6;Tsounta and Osueke 2014: 18–20.Thernborn 2013: 156 expresses concern about the “longterm political sustainability” of this process.
[31] Quote from http://www.azquotes.com/quote/917097.
历史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呢?我的回答是历史可以提供许多不平等的动态,但是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答案。让我们从此前的分析开始。集约型经济增长可能引起物质资源分配上的日益失衡,但物质资源分配失衡并不(总)是由其直接引起的。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在一些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实际不平等状况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但是,名义上的不平等最终是由产出规模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状况决定的:产出越多的经济体,资源越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尽管现实中不一定这样(其成立条件在附录中)。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基本联系体现在人类从觅食到驯养动物这一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第一次使得普遍的资源分配不平等成为现实,并且使情况趋于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与库兹涅茨式的转变不一致: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这一社会视为由部分觅食者和部分农民组成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应用暂时加剧不平等状况的双部门模型。更重要的是,人类从觅食向驯养动物的转变并没有给予人们实现平等化的希望。人类的定居、农耕和代际传承的物质资产的膨胀只是增加了潜在的和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而没有提供减少暴力冲击的其他机制。 [1]
驯养动物和农业(有机燃料)经济确立之后的几千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转变。这首先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受到了限制,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往往会引起现有不平等压力的上升。其次,缺乏矫正不平等的机制。这是因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可能逾越一定的阶段,这就使得做任何库兹涅茨式的转变都是不可行的。然而,经济变迁只是驱动不平等演变的一个因素。驯养动物增强了(国家的)强制力,助长了难以想象的、规模空前的掠夺行为。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日益扩张以及政治权力关系失衡加速使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大大缩减不平等程度是不可能的,除非暴力灾难短暂地取代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剥削结构和财产所有权结构。因为在前现代历史中,源自大规模群众战争或者革命的再分配政策非常罕见,冲击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是国家失灵或流行病。若没有这些冲击,不平等水平就会一直居高不下。在任何给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变幻莫测的国家政权更迭,各大洲之间的竞争,统治者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制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的程度。
从长期来看,历史记录表明,如果在上述(不平等程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外,探究不平等的变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系统性联系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在前现代社会,这两种主要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往往引起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尽管国家失灵或制度崩溃会减少人均产出,社会均等化的结果却是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但是,一些重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影响恰恰相反:社会均等化的结果是马尔萨斯约束软化,人均生产率水平提高,普通群众消费增加。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黑死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平等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欧洲经济充满活力时还是在其停滞不前时,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像早期的诸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它们的结构类似,但是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不一样。一般来说,在前工业化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演变过程中,政治权力关系和人口比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随后的从农业向工业、从有机燃料经济向化石燃料经济的大转型(工业革命)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社会不平等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转变之前特定社会中的不平等水平,但是,工业革命通常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形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和商品生产国中,随后被大规模战争和革命的暴力冲击终止。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状况就难以改变。直到1914—1950年的“大压缩时期”,我们都难以找到显著的、能充分证明的与暴力冲击无关的缩减物质不平等的案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前现代的例子似乎只局限于16—18世纪葡萄牙的部分地区,也可能包括17—19世纪中叶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在现代,瑞典,挪威,可能还有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国的突然衰落使我们很难预测其长期演变趋势。意大利的发展仍然很不确定,也难以对这一范例提供更多的素材。即使我忽略某些案例或提供出新的证据,毫无疑问,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现象在历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许多国家,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收入尤其是财富平等化已经持续了一代人左右。并且,这种矫正效果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一矫正过程通常很难(如果可能的话)摆脱极端暴力的根源。就连前几年看上去最有希望成为和平矫正范例的拉丁美洲,现在看来也不免令人失望。 [3]
(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不可能一直上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它会受到人均产出水平上限的约束,而人均产出在长期内相当坚挺:本书的附录探讨了其基本动力学。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发生暴力矫正不平等事件的情况下,相对于理论上的最大值,不平等水平通常处于高位,而且它还会在随后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在经济从暴力冲击中复苏的时期,在中世纪的繁盛时期(在欧洲是16—20世纪),在美洲的一个较短的时期,或者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现象。这些反复出现的趋势表明存在着适用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既适用于农业社会,也适用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既适合成长中的经济发展时期,也适合停滞的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趋同性凸显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跨文化研究和理论创建的必要性: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要合理地解释各种在断断续续的矫正之后,一再驱动不平等水平(紧跟)的各种力量,需要一本篇幅类似甚至更长的书去说明。
两个重要的问题仍需探讨:一是如果暴力冲击对减弱和逆转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暴力冲击就一定会出现吗?二是如果这些暴力冲击不发生,那么不平等会一直存在吗?第一个问题更为传统,这涉及对历史原因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反事实分析。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没有证据表明,前工业化社会内部包含发生实质性和平矫正的萌芽。但是,我们怎样判断对既定的权力、收入和财富等级结构的暴力破坏是随机的外生性事件,还是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度不平等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精英政策和权力不平等一方面使大多数前工业化社会极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社会最终的解体。一个大帝国的形成尤其如此:它不仅仅要面对外部挑战者,同时也要抑制国内精英企图吸收并占有社会剩余的贪婪,由此会剥夺统治者统一各个疆域的财富。在第2章,我已经提到中国和罗马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趋势。然而,借用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话说,对于这种稳定的相互作用,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确实触发了种种暴力,这些暴力通常具有破坏性,它们最后会使不平等水平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也会毁坏其他东西,其中包括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巨额的社会财富。很高程度的不平等水平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但它不会自行下降。恰恰相反,在此过程中,它会引起战争、社会冲突和革命,这些暴力会降低社会不平等。 [4]
“最终”的随意使用凸显了这种观点的严重缺陷:如果较高的不平等是人类文明所默认的条件,人们就容易推出这种条件与几乎已经发生的任何暴力冲击之间的联系——更难的是去解释这些类似的、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冲击没有发生或者缺乏这些冲击时会怎么样。
彼得·图尔钦是一位从人口生态学转向历史学的学者。他试图把国家失灵及其对平等化的影响理论化和内生化,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尝试。他的长期循环的综合理论描绘了一种典型的发展过程,即在一个大致可预测的时间框架内,宏观社会结构逐渐削弱,之后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增长给环境承载力施加了压力,降低了与土地有关的劳动力的价值。这一过程有利于精英致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反过来,这又会加剧精英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这一危机又反作用于如下人口动态学:减少人口压力,让现有的精英阶层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支持重建国家制度的军事精英的崛起。对历史案例的研究被用来检验这些预测,也突出了精英行为和围绕人口和财政因素的竞争的极端重要性。 [5]
这种内生化可能会降低诸如流行病之类的主要或完全是外生性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外生因素会受到社会条件(包括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影响,但绝不是由社会条件导致的。然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冲击可以被合理地内生化,从而产生一种关于收入和财富集中程度波动的更稳定的模型,这也并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主题。不管它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必要的冲击在本质上都是暴力的。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失衡、社会失衡和经济失衡的影响,这些失衡如何导致了实际不平等。这些失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能够更好地将暴力矫正不平等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由精英行为和人口引起的对建立国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叙述中。改朝换代的革命和国家失灵的案例就为检验这个命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想要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则需要单独写一本著作。就目前而言,我只想敲敲警钟。尽管精选出合适的例子去支撑长期循环理论或较完备的模型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这些观点最终需要依据其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文献能够佐证的程度来判断其优劣。
想想1800年左右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方的不平等程度要么很高,要么在上升。法国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案例,它先后经历了人口上升压力、精英的贪婪、使人痛苦的不平等和暴力终结不平等这样一个周期。长期以来,荷兰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一直在不断上升。反对君主制的一派借助于法国的武装干涉,宣布成立巴塔维亚共和国,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国内冲突的产物。其不平等状况可以用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来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的不平等程度也一直在上升,但没有引发任何重大危机。外国势力的多次入侵——这主要是一系列外生事件,势必要求极大地改变收入的分配状况。收入分配的改变反过来又引发了美洲南部、中部地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追溯到国内的紧张局势和半岛战争这一外生触发性因素。最后,英国也存在与所有其他社会相类似的物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它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国内动荡。把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变化或在战争中的表现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是,当我们考虑的复杂变量越多,应用连贯、清晰的内生性理论来解释广泛的现实案例则越困难。因此,我们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6]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如此。历史有其局限性。任何关于不平等的历史描述都必定聚焦于(我们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上,并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发现我很容易对此毫不在意。正如利奥波德·兰克在1824年多次引用的名言,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进行探索,则应该“如实直书”——那就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历史记录表明,暴力冲击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最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而非暴力机制通常无法产生类似的结果。然而,倾向社会科学的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反事实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地确定那些产生既定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得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通过暴力方式矫正不平等只是破坏了原本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来矫正不平等的社会,那该怎么办?
诚然,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难以找到。如果罗马帝国没有衰落,它的贵族会与被压迫的民众分享他们的巨额财富吗?如果黑死病没有发生,英国的劳工就能说服他们的雇主将他们的工资增加两倍或三倍?对这些问题或任何类似问题的回答肯定是“不会”。甚至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即通过和平机制可能也会引起同样的变化。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甚至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帝国通常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流行病注定会在某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发生。永不衰落的罗马帝国或没有瘟疫的世界都不是现实的反事实情境。如果实际的冲击没有发生,他们最终也会被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最近,仍然找不到一个可行的,能替代周期性的暴力矫正不平等的方案。
但是,如果现代社会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游戏规则,那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因为很容易找到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备选方案,比如大众教育、选举权的扩大、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工业时代的任何其他的新特征。公正地说,本书的观点一直是悲观的。对一个更乐观的观察者而言(比方说,一位经济学家会传播现代的库兹涅茨曲线,政治学家也避免依赖西式的民主和其他开明制度所产生的荣耀),现代三十年战争的动荡及其持久的影响仅仅先于由现代社会的各种福祉所带来的和平、有序和完全内生化的平等。这段历史没法拒绝为这个事情提供必要的澄清,严格地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事实,但是仍有必要深入地探究这种特定的反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那世界将会怎样?一个完全和平的20世纪似乎是一个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反事实分析。鉴于当时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的事实和主要欧洲国家性质及其统治阶级的特征,某种程度上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反事实分析并不能解释战争开始的时机或者持续时间和战争的惨烈程度——至少难以解释在“一战”结束之后,新的冲突爆发又是如何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7]
从理论上说,我们希望能够研究两个不同的西方世界,即一个被全面的战争和萧条的经济摧毁的西方世界,以及一个毫发无损的西方世界。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能假定生态和制度不变,从而只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自然实验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实验是不明智的,对卷入战争的人来说则是悲惨的。顾名思义,世界大战是指战争囊括了非同寻常的地理范围。因此,反事实预测逼近现实世界状态的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尽管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和日本都以相对较低的限度的方式参加了“一战”。在正式参战的19个月和时间明显更短的作战中,美国参与的时间很短,其征兵率仍然比欧洲国家低得多。日本的贡献更是微不足道——不仅是相对于其他参与国家,而且相对于10年前和俄罗斯的高风险战争都是如此。与欧洲主要的交战国不同的是,美国、日本的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短暂的,之后不平等程度日益回升。
“二战”比“一战”在全球内波及的范围更广,可供我们选择的国家更少。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找到那些没遭受重大损失或未受重大影响的发达国家似乎是不可能的。瑞士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份额只有轻微、短暂的下降,并且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自1933年开始报告以来一直相对稳定。我们只好选择最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他们在制度和生态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只能指望这些国家了。显然,阿根廷(就像南非一样)在“二战”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并且,在矫正不平等和财政扩张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在1945年之后,由于外国的干预,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对于不发生全民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矫正不平等的重大举措这一观点,我们现有的证据少得可怜。 [8]
当然,这个猜想离定论还很远。人们有理由认为工业国家如果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我们暂时把整个20世纪想象成一个没有暴力冲击的世界,或者设想所发生的这些战争迅速结束,并且导致新的持久的权力平衡——这一点有点不可信,那么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将会如何演变呢?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资本的破坏和贬值,激进的财政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干预,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将不会像1914年—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样大幅下降。人们所观察到的矫正不平等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根本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反事实机制能够在一代人的时期内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但是反过来的话,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考虑一下囊括整个20世纪的4种理想情形的典型结果(图14.1中1~4)。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悲观”的情形是一个具有19世纪特征的模式的延续。在欧洲,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黑死病的结束时期;在美国,至少可以上溯到其独立之时。在此期间,收入和财富先后经历了逐渐上升和日益集中的两个阶段。在那个时候,西方(和日本)的不平等水平一直很高,但相对稳定,一个永无止境的镀金时代被根深蒂固的富豪控制。在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水平可能上升更多,而其他一些原本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和,最突出的是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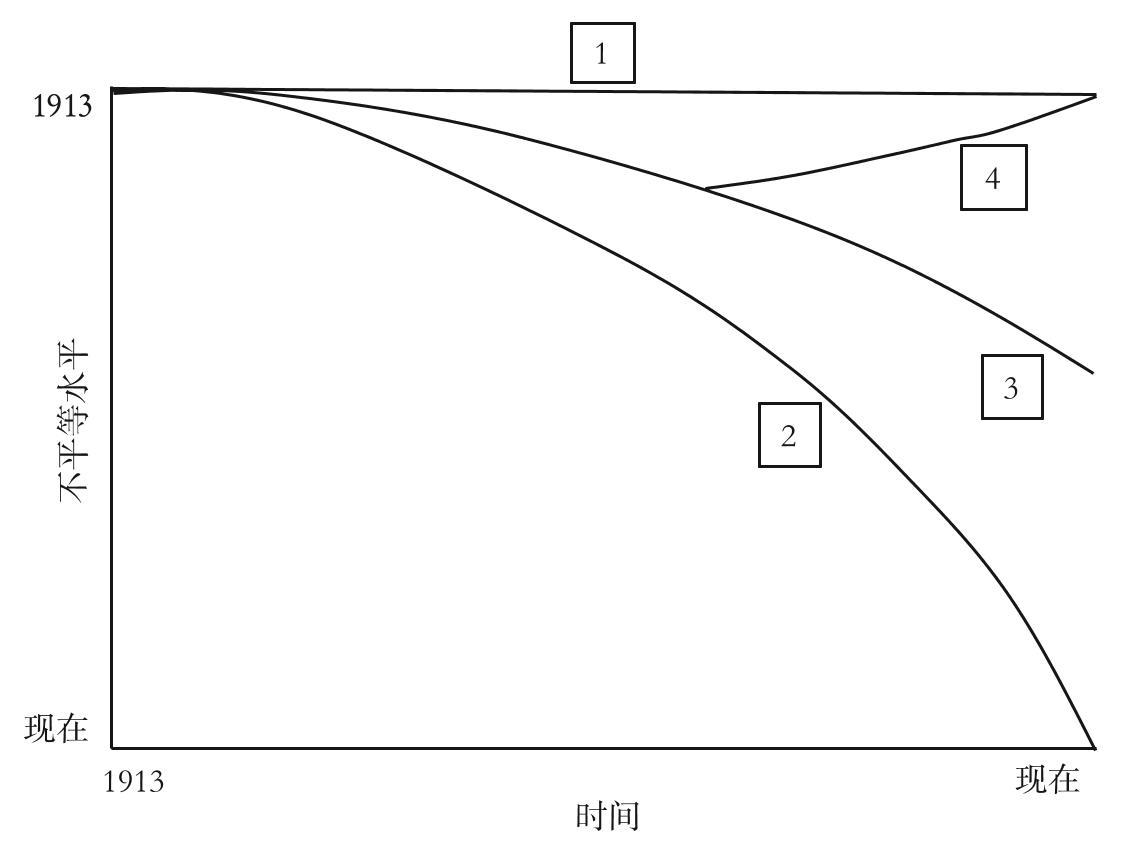
图14.1 20世纪反事实分析的不平等的趋势
这一结果虽然在前现代历史中长期稳定的时期内是非常现实的,但在20世纪出现显得过于保守。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社会保障立法和收入或财产税,扩大选举权,并允许组织工会。尽管这些努力还没法达到后来几代人的标准,但是他们为后来大约两代人推进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基础。在我们反事实分析的和平世界中,这些政策想必也会继续实施下去,尽管速度会有所放缓。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
但是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不平等呢?第二个情形是最“乐观”的反事实分析。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政策和大众教育会慢慢地促使收入和财富逐渐分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良性过程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赶上了几十年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时期或整个时期所经历的不平等水平。然而,如果假设不经历一个暴力引起的“大压缩时期”,稍后的不平等程度将最终会以类似的规模减弱,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假设结果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作用有关。虽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国家通过调整财产税和干预市场经济来蚕食资本收益,但是很难想象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资本会在类似的规模上被摧毁和贬值。既然20世纪的平等化是一种重要现象,不管耗时多长,较小破坏性的环境会使整体不平等大幅度下降变得更加困难。
在我们和平的反事实分析中,不太可能实施现实生活中其他的措施:边际所得税率超过90%,征收财产税,对商业活动和资本回报率进行大规模国家干预——比如对工资、租金和股息等方面的管制。也不会发生那种灾难性通货膨胀,那种通货膨胀已经消灭了几个国家的食利者。我们也需要消除共产主义的收入均等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1945年之后的中欧和1950年之后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中,而且还间接体现在这些国家对西方和东亚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惩罚措施上。最后,一个和平的反事实世界不会出现类似于1914年之后的全球化进程的中断。全球化的中断会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并且促成各种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各种其他的管制。在现实世界中,“二战”之后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克服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影响。通过一些措施的实施,全球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完全恢复。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过去150年连续的、真实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再加上迟来的或许还不完全的非殖民化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精英所带来的意外收获。 [9]
考虑到反事实分析中缺少这些强大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最合理的结果似乎是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规模比实际历史中的规模更小(多小?)。即便如此,第三个比较“折中”的情形也可能过于乐观了。如果我们假设反事实世界中的技术进步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进步(在长期看来这是合理的),则不会有那么多使当代观察家苦恼的关于不平等的压力。从技术进步到计算机化使复苏的部门收入分化到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直到不平等下降到接近我们现实世界的水平之前,他们才会感受到这些压力,而且那些没有受到世界大战的暴力冲击的社会,难道也没有能力顶住这些冲击?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情形是,由于社会民主和大众教育削弱了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不平等水平在20世纪的中间50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那之后又出现了反弹,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确实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4个反事实结果中最合理的一个),不平等水平可能已经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常见的水平,这使我们处于一个比目前发现的更糟的境地(图14.1)。
虽然对这些理想、典型的反事实的相对价值做更长远的思考是徒劳的,但这会帮助我们理解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实施了真正的矫正不平等的措施,则会有多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循序渐进地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平等的可行性,即使几乎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第二,我们必须假定还存在一个处在相对和平条件下的世纪:任何比较严重的反事实冲击,无论其时间和细节如何,将会使我们回到真实世界,但强化了通过暴力实现平等的优势。第三,我们需要假设,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暴乱,20世纪早期存在的资本积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当然,这需要更大地发挥你的想象力。第四,我们必须相信任何平等都不会被我们观察到的上一代人的不平等力量逆转。前三个条件必须适用于所发生的、所有重大的、非暴力方式实现的平等,而这4个条件都要求不平等水平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程度大体类似。这是一大难题,它强烈地表明,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暴力冲突,发达国家目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会远远高于如今的水平。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它到底高出多少。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一观点无关紧要,不仅是因为它不可能被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回事。但这样想是错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平等的反事实分析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而显得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在不发生大压缩的全球暴力时,不平等现象会否减少,或有多大程度的减少,我们该如何判断目前以及未来的平等化前景呢?相对于所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区域性危机,在我的反事实分析中概述的相对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今天大多数人所生活的世界。这些条件是如何影响当前的不平等状况的,它们对未来的矫正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此处和接下来的4个段落,我总结了导言中的基本观点,然后进一步详细阐述。
[2] 关于早期的现代欧洲国家,参见本书的第3章。米拉诺维奇在其2016年的著作中也反对那种“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观点。
[3] See esp.herein, chapter 3, pp.164–173 and chapter 13, pp.382–383, 387.
[4] Quote: Milanovic 2016: 98.In 1790, Noah Webster considered Rome’s “vast inequality of fortunes” to be the principal cause for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Miscellaneous remarks on divisions of property ...,” http:// press-pubs.uchicago.edu/founders/print_documents/v1ch15s44.html).
[5] The clearest exposition of secular cycle theory can be found in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6–21.Cf.also 23–25 for more rapid and elite-centered cycles in polygynous societies, and see 303–314 for the results of existing case studies.Turchin 2016a applies an adapted version of this model to the United States.Motesharrei, Rivas, and Kalnay 2014 present a more abstract model of how elite overconsumption may precipitate the collapse of unequal societies.
[6] Turchin and Nefedov 2009: 28–29 only briefly acknowledge exogenous factors.This can be a serious problem, most notably in the case of the Black Death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which defies endogenization: 35–80.For the societies mentioned in the text, see herein,chapter 3, pp.94–101.Note that i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lbertus 2015: 173–174 finds no connection between particular levels of land inequality and land reform or collective action leading to land reform.
[7] 在此,我忽略了有关1914年全球冲突爆发原因的争论。这一争论近百年来越来越受重视。需要注意的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大战内生于现代发展过程中,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世界大战,大规模动员是当时武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21–22.But this did not by itself determine the odds of actual war.Milanovic 2016: 94–97 proposes a more specific link between inequality and World War I that would allow the resultant leveling to be “‘endogenized’ in economic conditions predating the war” (94).
[8] World War I: WWID.World War II: for putative bystanders, see herein, chapter 5, pp.158–164.Switzerland: Dell, Piketty, and Saez 2007: 474;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34–535, 545; and herein, chapter 5, pp.158–159.For Argentina, see herein, chapter 5, p.156.
[9] For the disequalizing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see herein, chapter 15, pp.413–414.British colonies in Africa tended to be quite unequal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even though inequality had in some cases already been declining in the postwar period: see Atkinson 2014b.For the importance of colonial assets for some European wealth elites, see Piketty 2014: 116–117 figs.3.1–2, 148.
经历过大压缩时期的最后一代人也即将全部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二战”中服役的95%的美国人都已经离世,那些还活着的人大多数已经90多岁了。与人的死亡一样,大的矫正作用也不复存在。在发达国家,始于1914年的不平等程度的巨幅下降已经走到了尽头。以10年算一代人的话,大约在一代人之间,所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增加了。对此,我们有可靠的数据(见表15.1和图15.1)。 [1]
表15.1 1980—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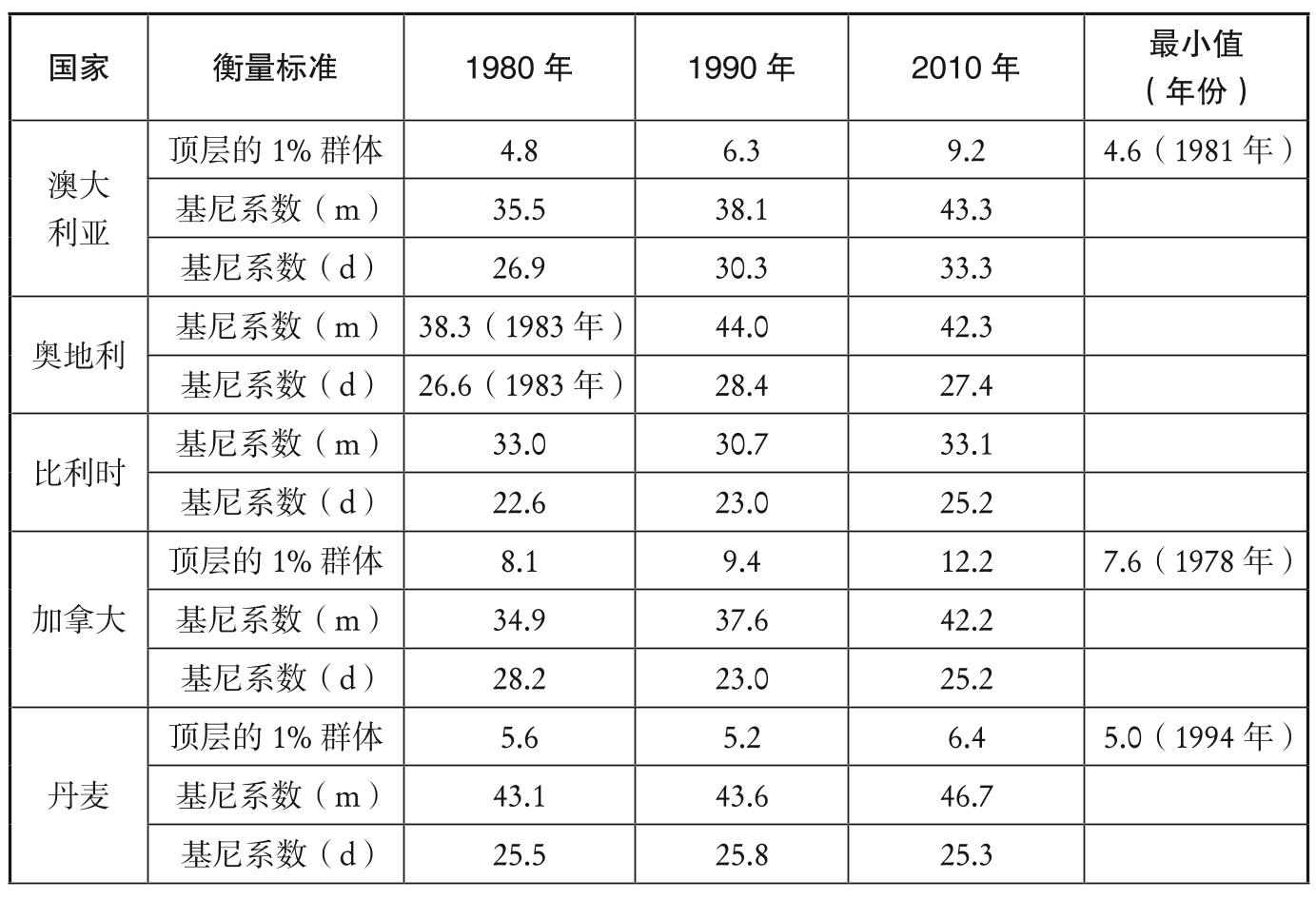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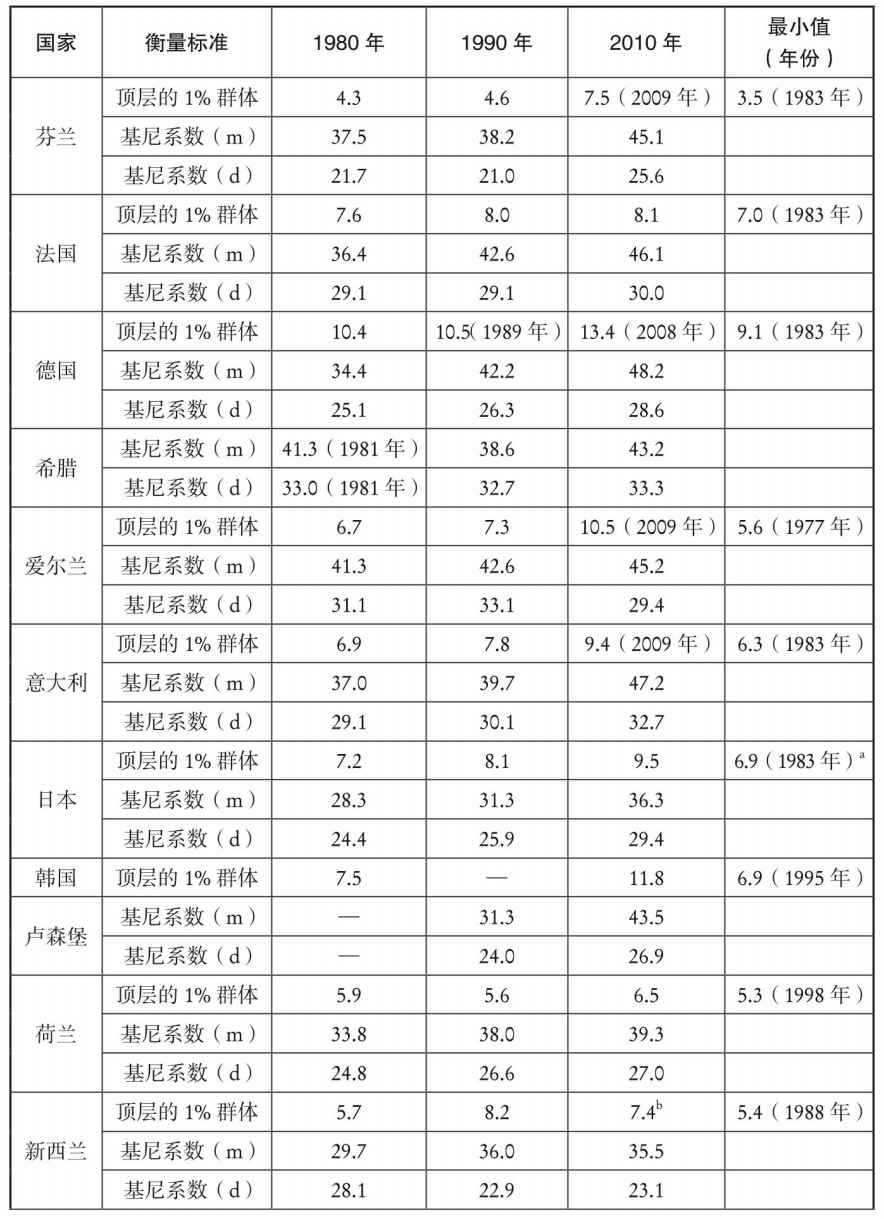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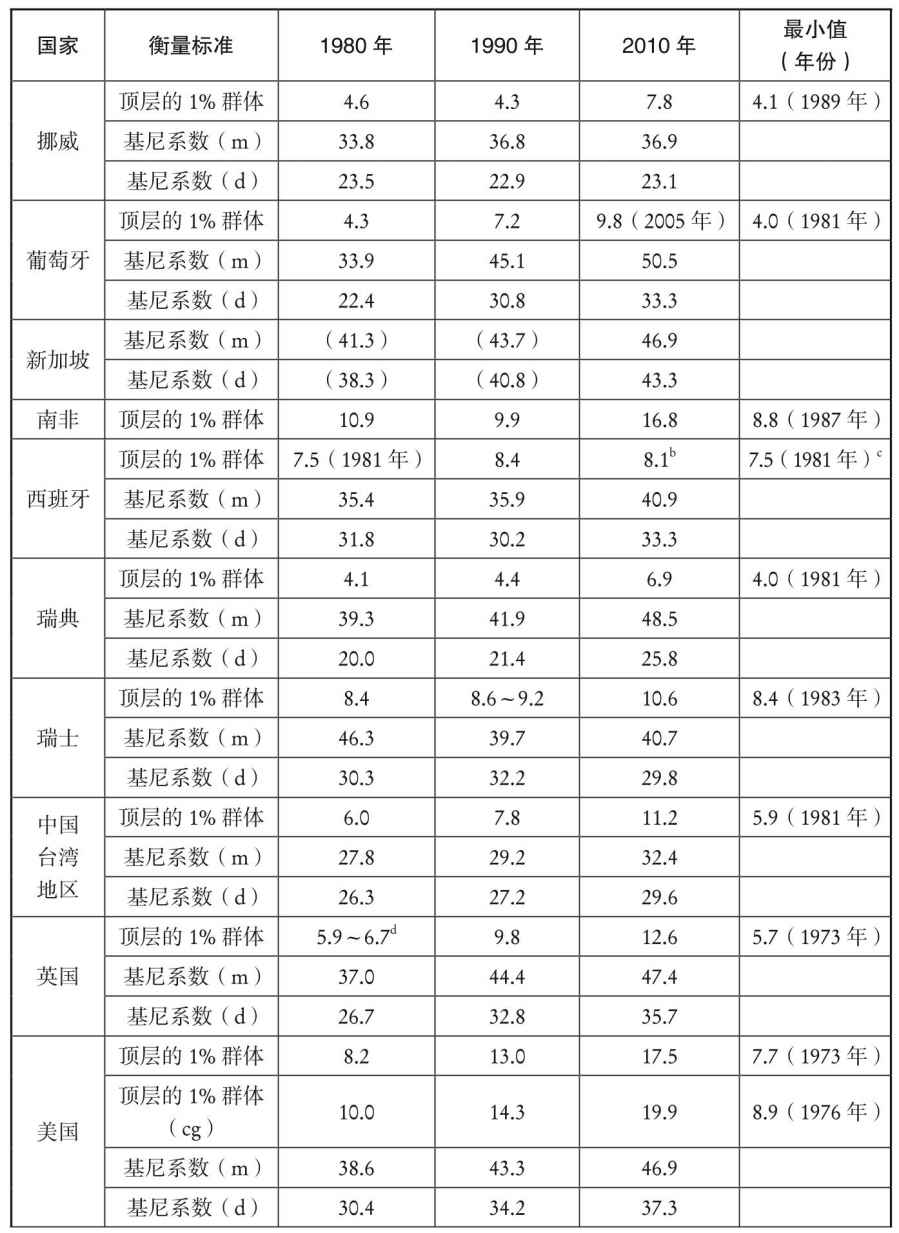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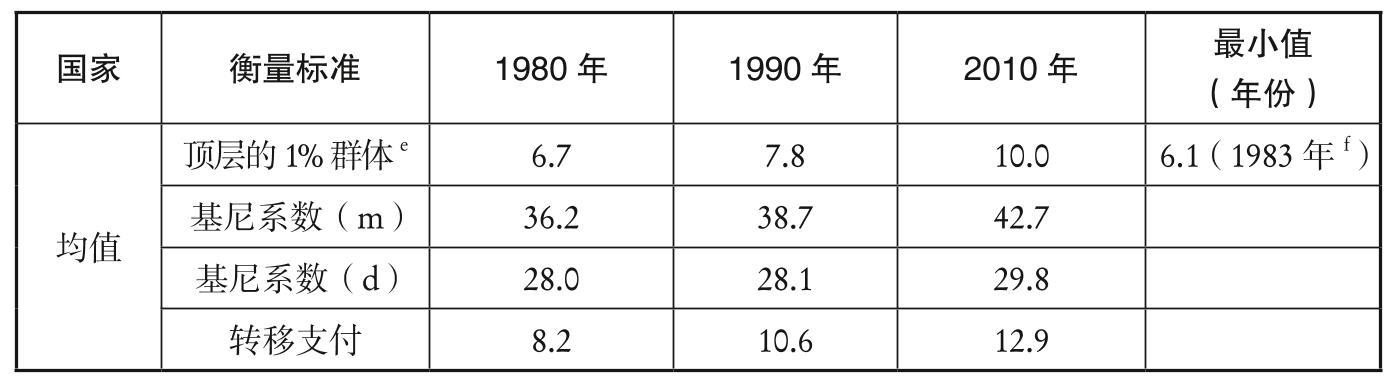
m=市场收入,d=可支配收入,cg=含资本收益
a 1945年为6.4。
b 见本章注释3。
c 1980年以前的数据缺失。
d 1979—1981年。
e 不包括南非的情况。包括南非的情况:6.9(1980年),7.9(1990年),10.3(2010年),6.2(最小值,1983年)。括号内的结果基于不确定的数据。
f 中位数和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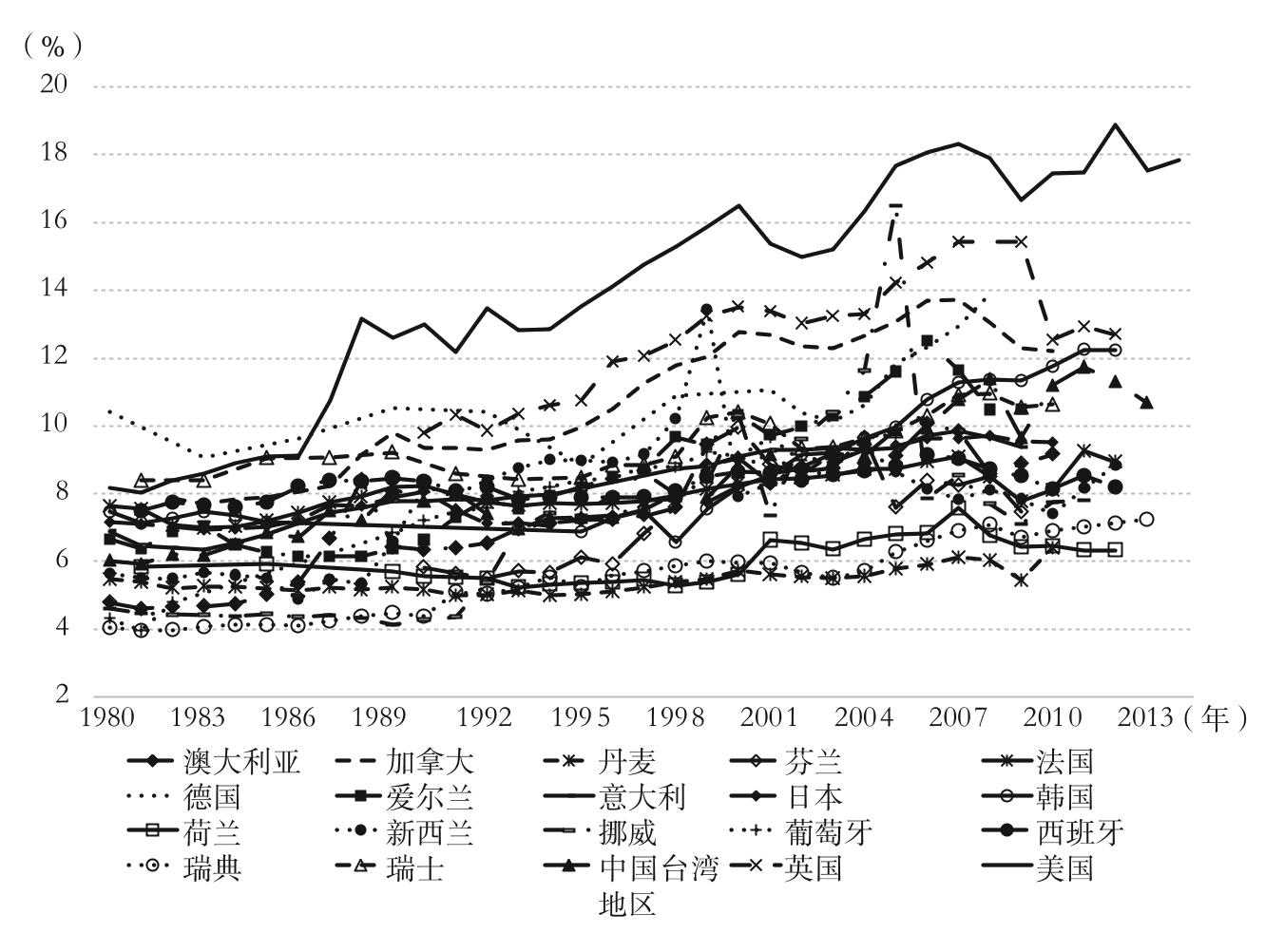
图15.1 20个OECD成员1%的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1980—2013年
在一个由26个国家所构成的样本中,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在1980—2010年增长50%,同时,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只有通过一个几乎是全面的再分配转移支付才能部分地消除这种结果。从统计指标看,198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士的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在这一年逆转了,这也代表了整个样本的信息。盎格鲁–撒克逊人引领了这个趋势,它们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英国的不平等水平在1973年开始上升,美国则在1973年或1976年,爱尔兰在1977年,加拿大在1978年,澳大利亚在1981年。美国人的工资离散度在197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扩大。其他的测量结果也确认了这一事实。等值可支配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和高收入者相对低收入者的收入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普遍提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OECD成员中,获得中间收入的人口比例相对于那些获得高收入或低收入的人口比例来说都下降了。 [2]
更仔细地看,这个趋势几乎完全不存在哪怕是部分的例外。由于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统计了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的数据,因此,我在表15.1中使用了单一基准年的处理方法,这一方法使得西班牙和新西兰的不平等水平看起来好像有轻微的下降,法国保持不变。如果我们改用5年移动平均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左右以来,在这一组国家和地区中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高收入者收入份额都至少有轻微的上升。用同样的方法来追踪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除澳大利亚、爱尔兰和瑞士之外都上升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平等水平无一例外地都上升了。绝大多数情形下,收入集中变得更加明显:在21个公布了最高收入份额的国家和地区中,11个国家和地区收入最高的1%群体获得的收入在1980—2010年间上升了至少50%,有的上升了100%以上。 [3]
在2012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甚至创造了几项纪录:在这一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无论是否含有资本收益)和最富有的0.01%的家庭所拥有的私人财富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192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所报告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很有可能低估了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因为它们是从难以获取最富有家庭信息的调查结果中推导出来的。就美国而言,各种调整都将带来基尼系数的显著上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会如此。因此,在1970—2010年间,官方的市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从0.4上升到0.48,而实际可能是,197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0.45左右,到2010年则高达0.52~0.58。也就是说,即使最保守的修正结果也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指数从1970年的0.41上升到2010年的0.52,上升比例超过了25%。再分配只是非常轻微地缓和了这个趋势:1979—2011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3.82%,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后,这一比例为4.05%,那些收入最低的20%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46%,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年收入增长率则是1.23%。 [4]
这个趋势绝不仅仅局限于表15.1所考察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正如我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形式上或实质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都经历了物质不平等水平的大幅提升。这种发展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涨了不止一倍,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相应的财富集中度系数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基尼系数甚至更低,只有0.27。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印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44~0.45上升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1,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9年间翻了一番。巴基斯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70年前后0.3的低水平上升到2010年的0.55。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分辨出一个连贯的长期趋势。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它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收入集中化运动中恢复过来,但它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依然比1980年前后的水平要高。在第13章,我曾记录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复杂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状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世界各地收入最高的20%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都扩大了。 [5]
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化的情形。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产出未能超过苏联时期水平的俄罗斯,榨取率提高了一倍。更普遍的现象是,由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欧、东欧以及中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只不过东亚是受到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2002年前后的拉丁美洲,则是受宏观经济危机和结构转型的驱动。这些国家以外的西方富裕国家的类似变化被归咎于其他一整套原因。 [6]
除了拉丁美洲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经历了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时期及其带来的温和的平等化的余波。直接参与世界大战的国家现在占全球名义GDP的3/4以上,当我们将欧洲的旁观者和受到重大影响的前殖民地纳入考虑时,这一比例增长到4/5以上。因此,最近的不平等水平普遍上升或许最好被理解成对早期暴力冲击造成的低到异常水平的平等化(也许不可持续)的削弱。
我从对人类起源到20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演变的概述中开始了本书。从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中进行抽样,我把资源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这种掠夺性行为是指那些强势者拥有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至他们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可能获得的财富——这是经济学家称其为“租金”的东西。这些机制至今仍然活跃。从本质上看,当前关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的争论,往往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即通过供给和需求运作的市场力量与制度和权力关系,两者哪个更重要。虽然极少有严肃的观察者否认所有这些都是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日益增加的显著原因,但具体细节仍然被激烈争论。近年来,当供求范式的支持者一直在设计强调技术、技能和有效市场中心地位的更加复杂的模型时,制度和基于权力的解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7]
许多观察者将不断加深的贫富差距归因于高等教育的高回报率,特别是在美国。1981—2005年,高中毕业生和继续接受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从48%上升到97%,翻了一番。这种发展远不止是收益的不平衡:1980—2012年,男子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0%~56%,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收益最大,而高中毕业生的收益减少了11%,高中辍学的人的收益则减少了22%。1980年左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大约2/3的工资离散度增大归因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所得到的扩大的溢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工时占所有工时的比例迅速提高,这一提高从1982年开始放缓,由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超过技术工人的供给,工资溢价上升了。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动化代替原来通常的人力劳动,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生产,对正规教育、专业技术和认知能力的需求普遍提高。这导致了低收入、手工密集型职业和高收入、抽象密集型职业的两极化,因为中级职位被取代了,因而收入分配的中间层变空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去平等化后果。 [8]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被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案。2004—2012年间,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供应量再次上升,同时工资溢价保持平稳(维持在高水平)。除英国之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几个东亚国家的技能溢价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受教育工人的供给水平有关。事实上,各国的教育回报率差异很大:美国的教育回报率高达瑞典的两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更高的教育溢价与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 [9]
即便如此,批评家也指出了这种解决方案的各种局限。高收入职业和低收入职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证据支持,技术变革和自动化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比率的变化。相反,职业内部而非职业之间的收入变化似乎是不平等的关键驱动力。此外,最高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很难用教育来解释,我后面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复杂的是,美国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不匹配情况日益增加,因为工人所受的教育越来越超过他们的工作需要,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日益增大的工资离散度。 [10]
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长期以来,其消长都与不平等的波动有关: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与正在上升或保持稳定(并且处于高水平)的不平等状况相吻合——不仅在西方,在拉丁美洲和日本也是如此,不平等在1914—20世纪40年代由战争和大萧条引起的全球化中断期间得以下降。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趋势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同时发生的放松管制显著提高了不平等程度。尽管全球化通常有利于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却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这种失衡有几个原因。根据一项估计,印度市场改革和苏联集团的垮台,使得全球经济体中的工人数量翻了一番——资本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并且全球劳动力中的技术工人大比例下降,从而扩大了富裕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程度。以国外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金融全球化给技能溢价增加了压力,也可能对资本回报产生了压力,并在较高收入区间的人之间引起了不平等状况。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在成品贸易上的竞争似乎对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影响不大。贸易全球化的平等化效果与资本全球流动的非平等化效果相互竞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产生了种种中和效应,从而降低了总体效应。 [11]
全球化也能影响政策决策。白热化的竞争、金融自由化和消除资本流动障碍,都可能会鼓励财政改革和放松经济管制。因此,全球化将税收从对企业和个人课税转移到课征支出税,这趋于增加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便如此,至少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竞争在理论上只会限制某些类型的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没有普遍地减少福利支出。 [12]
在富国,人口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移民对美国的不平等影响不大,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带来了平等化的结果。相反,门当户对的婚配——更具体地说,婚姻伴侣双方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似性扩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被认为在1967—2005年间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总体提高25%~30%,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 [13]
制度变迁是另一个罪魁祸首。工会会员率的不断下降和最低工资的下降一直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再分配与工会密度和集体工资谈判正相关。劳动和就业保护组织越强大,越会降低技能回报率。一般来说,工会成员倾向于通过制度化的公平准则来压制工资不平等。相反地,反工会化和实际最低工资的向下压力明显导致收入分配的偏化:1973—2007年间,美国男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34%下降到8%,女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16%下降到6%,同时每小时工资不平等程度提高了40%以上,占这一时期总体不平等现象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其规模类似于技能溢价的上涨。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与此同时,欧洲大陆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限制不平等上升方面更加有效。 [14]
正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助于确定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一样,财政机构在确定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二战”期间和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收入的边际税率飙升至历史新高。在收入不平等开始复苏时,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对18个OECD成员的一项调查发现,除两个成员外,其他成员的最高边际税率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与税收负担高度相关: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那些经历了大幅减税的国家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财产税的规模也趋向于同样的方向:尽管巨额遗产税阻碍了战后时期的巨额财富重建,但随后的减税措施促进了新的财富积累。在美国,更低的资本所得税已经提高了资本收入占总体税后收入的份额,伴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减税,资本收益和股息的相对权重也大幅上涨。1980—2013年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的平均所得税率从42%下降到27%,平均财富税率也从54%下降到40%。税收累进度的减少解释了最近美国财富离散度的近一半的增长,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多数OECD成员的再分配规模增加了,但税收和转移支付没有跟上日益增长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步伐,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再分配已经成为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平等化手段。 [15]
由于税收、商业管制、移民法以及各种劳动力市场制度都是由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所以上述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牢固地根植于政治领域。我已经提到过,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影响国家级的立法成果。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在美国,两大党派都转向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对记名投票的分析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右翼程度要比民主党的左翼程度大,但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金融放松管制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别、种族和性认同等文化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国会政治的两极分化在20世纪40年代触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1913—2008年间,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的变化与两极分化的程度密切相关,但大约滞后10年:后者的变化先于前者,但二者一般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先下降,然后上升。与美国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相比,金融部门的工资和教育水平也是如此,这一指数同样滞后于党派两极分化。因此,一般来说,精英收入,特别是金融部门的精英收入,对立法凝聚力的程度高度敏感,并受益于日益恶化的政治僵局。
此外,富裕家庭更加愿意参与选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太富裕的选民投票率通常都很低,这已经被大量非公民低收入工人群体的大规模移民放大。在2008年和2010年的选举中,选民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其特点是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呈现出线性增长:2010年,最贫困的家庭中只有1/4投了票,而那些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中,半数以上都投了票。在税收、监管和社会福利方面,美国的1%群体与总人口相比在政治上更加积极或更加保守,在收入等级最高的群体中这种扭曲表现得更加强烈。最后,尽管分项捐款数量大幅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竞选捐款越来越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顶层的0.01%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占总捐献竞选资金的10%~15%,到2012年占到总数的40%以上。因此,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献者,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可观察到的倾向——立法者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高收入选民偏好的政策。 [16]
所有这一切充分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权力关系的转变一直在补充并加剧由技术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非平等化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最顶层群体的变化对体制和政治因素尤为敏感,有时还会带来戏剧性的后果。在美国,1979—2007年间市场收入增长的60%被1%的顶层群体吸收,而总增长中仅有9%的收入落入90%的底层人手中。同样,精英集团占有税后收入总增长的38%,而80%的底层人群仅占有31%。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顶层0.0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份额翻了一番。收入差距一直集中在较高的收入等级: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第9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50百分位的收入的比率一直在增长,第5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1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的比率(中间层对底层的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相当平稳。换句话说,高收入者从其他人那里拿走金钱。这种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十分典型,在大多数其他OECD成员中则弱得多,甚至不存在。即便如此,从长期来看,总体收入不平等对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敏感可以说是普遍规律:在一些国家中,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顶层1%群体之下的那9%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约为20%~25%),而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一直在变化。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较高的财富份额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最大收入的相对规模是总体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值得特别注意。 [17]
为什么收入最高的人会得到远超其他人的收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解释。一些解释侧重于经济因素,如更高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特定管理技能的需求增加,擅长操控公司董事会的经理对租金的提取以及与资本收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另一些解释强调政治原因,如偏向保守政策的党派统治和政治影响,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降低税率,或强调社会进程的作用,如采用标杆管理,用偏高的标准或以野心勃勃的人为榜样来设定上层工资,以及社会规范和公平概念的变化。尽管制度上的原因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强调供求的解释被证明很有道理。用市值表示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使管理能力上的细微差别变得非常显著:因此有人声称,1980—2003年间,大公司股票市值的6倍增长可以充分解释美国CEO(首席执行官)薪酬的同期的6倍增长。在“赢者通吃”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本身有望为最顶层提高薪酬。
然而,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长期成立,即使在最近几十年,最高收入层的收入不成比例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司管理层和其他“巨星”的:在美国,高层管理人员、明星艺人和运动员精英只占最高收入人群的1/4。对相对较小的CEO群体来说,压力管理是个合理的解释,很难说清其他职位更大的加薪力度。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变革的效应和一些企业日益扩大的全球规模效应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绩效最高者的相对生产力提高,这与他们收入份额不断膨胀的情况相一致。 [18]
然而批评家有力地争辩说,“强烈影响财富的因素与经济生产率联系很少甚至没有关联”。在金融部门,薪酬水平与放松管制密切相关,但高于仅由可观察因素所能解释的水平。尽管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金融工作者与其他部门工作者一样得到了考虑教育因素调整后的工资,但到2006年,他们享有50%的工资溢价,高管的收入溢价则高达250%或300%。这种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的这种不成比例的收益意味着他们在拿走租金,即超过使竞争市场运行所需收入的部分。以2012年的美元标准计算,1978—2012年间美国CEO的薪酬上涨了876%,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的344%和389%的涨幅。20世纪90年代,美国CEO的薪酬与最高的收入和工资相比也急剧增长。
与需求有关的教育供给无法解释这些发展,也无法解释同一教育群体内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在一些最有利可图的就业和商业活动领域,社交技能比正规教育更加重要,高层管理者的价值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其所处的关系网来衡量,这种由消费者、供给者和管理者构筑的不可转让的关系网正是企业需要获得并控制的。连锁反应也值得关注:尽管高管薪酬的飙升和经济的“金融化”只对近期最高收入增长的一小部分负有直接责任,它们对法律和医药等其他行业的影响却扩大了它的不平等效应。此外,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已经受益于OECD成员边际最高税率的削减,给予优质工人优惠待遇的做法也超越私人行业进入公共领域。尽管大量财富的创造往往归功于政治影响力和掠夺性行为,权力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中更加重要。
最后是资本。因为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它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总是高于收入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所以,资本收入的相对重要性或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资本卷土重来是皮凯蒂近期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一趋势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国家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的复苏中,而二者的比例曾在大压缩时期急剧下降。从那时起,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财富的相对规模都大幅增加。类似的趋势也提高了私人财富与国家收入以及私人资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这种发展对不平等状况的整体影响仍然具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大部分的这种增长反映了私人住房价值的上涨,并且住房对资本存量贡献的计算方式的调整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个主要经济体资本与收入比保持稳定而非上涨。尽管在此期间,一些OECD成员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上升,但在20世纪70年代—21世纪早期的这段时期内,最高收入阶层的资本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相对权重并没有以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 [19]
财富的不平等状况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挪威、瑞典和英国的最富有的1%家庭的私人财富占有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荷兰的下降了;芬兰的有所上升,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幅上升。美国财富集中的速度甚至比美国收入集中的速度还要快。这一过程在极其富有的人中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2012年间,1%最富有人口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所占的份额上升了几乎1倍,但在最富有的0.01%人中上升了3倍,最富有的0.01%家庭中上升了至少5倍。这对资本收入的分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群体的所有应税资本收入占全国总量的份额从1/3增至2/3,几乎增加了一倍。2012年,这群人索取了3/4的股利和应税利息。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是,这群人中收入最高的0.01%家庭获得的利息份额从1997年的2.1%增长到2012年的27.3%,增长了12倍。 [20]
这些变化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2001—2010年间,资产净值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1上升到0.85,金融资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5上升到0.87。尽管工资分配和资本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收入最高的那1%的工资收入的相对重要性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所得对于高收入者变得更加重要,较低的税收增加了它对税后收入的贡献,更大一部分的精英现在也完全依赖于投资收入。1991—2006年间,资本收益和股息的变化对税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至关重要。 [21]
尽管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尤为突出,日益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现象。在1987—2013年间,超级富豪(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是由世界上每2000万富人中最富有的1人或者是地球上每1亿人中最富有的1人构成的群体)的财富平均每年增长6%,而全球成年人的平均增长水平为2%。此外,据估计,目前世界上8%的家庭金融财富都是存放在境外避税天堂,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未被记录。考虑到富人一定会不成比例地使用这种做法,并且美国人的资产中估计的海外持有比例(4%)远低于欧洲的(10%),因此,表面上更加平均的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可能比税收记录显示的高得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在海外持有的资产份额可能更大,以俄罗斯为例,可能多达国民私人财富的一半。 [22]
*
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在世界范围内的卷土重来与本书最前面的几章所叙述的不平等状况几乎无缝对接了。这部分所考察的许多变量都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作为提高不平等的强大驱动力,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在19世纪由大英帝国所推动的第一次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出现,后来又在美国的实际霸权下重新被确立,由于“冷战”结束而进一步加强。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诸如工会化、政府干预私人部门工资的制定以及高度累进的收入和财富税等关键的平等化机制开始崭露头角,“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充分就业也是如此。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政治的两极分化现象迅速减弱。虽然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起反向平衡作用的教育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归根结底,过去几十年里,不平等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反映了自大压缩以来国家关系和全球安全的演变:在暴力冲击破坏了全球交换网络,促进了社会团结和政治凝聚力,维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对它们的削弱已经开始侵蚀抑制收入差距和财富集中的这些机制了。 [23]
[1] Table 15.1 and Fig.15.1: WWID, SWIID.
[2] See Table 15.1.For the role of transfers in preventing a much steeper increase in disposable income inequality, see, e.g., Adema, Fron, and Ladaique 2014: 17–18 table 2; Morelli,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43–645; and cf.also Wang, Caminada, and Goudswaard 2012.Wage dispersion: Kopczuk, Saez, and Song 2010: 104 fig.I (the wage Gini increased from 0.38 in 1970 to 0.47 in 2004); cf.also Fisher, Johnson, and Smeeding 2013 for parallel trends in U.S.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up to 2006.Equivalized Ginis and S80/S20 and P90/P10 ratios: 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35–640.Hollowing out of the middle class: Milanovic 2016: 194–200, esp.196 fig.4.8, for minimal changes in Canada, Germany, and Sweden, modest ones in Spain, and more pronounced shrinkage in Australia, the Netherlan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Kingdom.For further summaries of these trends, see Brandolini and Smeeding 2009: 83, 88, 93–94; OECD 2011: 24 fig.1, 39 fig.12; Jaumotte and Osorio Buitron 2015: 10 fig.1.Wehler 2013 devotes an entire book to rising inequality in Germany, a country that has so far been relatively successful in containing this phenomenon.
[3] In Spain,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s averaged 8.3 percent from 1988 to 1992 and 8.4 percent from 2008 to 2012; in New Zealand, 7.3 percent from 1988 to 1992 and 8.1 percent from 2008 to 2012; and in France, 8 percent from 1988 to 1992 and 8.5 percent from 2008 to 2012.Between 1980 and 2010,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s rose 51 percent in Canada, 54 percent in South Africa, 57 percent in Ireland and South Korea, 68 percent in Sweden, 74 percent in Finland, 81 percent in Norway, 87 percent in Taiwan, 92 percent in Australia, about 100 perc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99 percent to 113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WID).
[4] 在美国,剔除资本收益,1929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年收入增长了18.4%,2012年为18.9%,而包含资本收益的情况下分别为22.4%和22.8%。最新获得的数据显示,2014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年收入增长,在剔除资本收益时为17.9%,包含资本收益时则为21.2%,这些数据相对于前几年都略微有些下降(WWID)。Top wealth share:Saez and Zucman 2016: Online Appendix table B1.The fact the wealth share of the richest 1 percent has not (yet) returned to 1929 levels shows that there is now more stratification within elite circles than there was then.Gini corrections: 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79 and esp.682 fig.8.28.Taxes and transfers: Gordon 2016: 611 table 18–2.
[5] For Russia and China, see herein, chapter 7, pp.222, 227.India, Pakistan, and Indonesia:SWIID, WWID.For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ee herein, chapter 13, pp.377–387.Global trends: Jaumotte, Lall, and Papageorgiou 2013: 277 fig.1, 279 fig.3.
[6] Russia and China: Milanovic 2013: 14 fig.6.Macroregional trends: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 790; and see also Ravaillon 2014: 852–853.
[7] Recent surveys of the literature include Bourguignon 2015: 74–116, esp.85–109; Keister 2014: 359–362;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46–567; and above all Salverda and Checchi 2015: 1593–1596, 1606–1612.Gordon 2016: 608–624;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227–241;and Milanovic 2016: 103–112 are the most recent summaries.
[8] Earnings gap: Autor 2014: 846; see also 844 fig.1 for an increase inthe median earnings gap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graduates from $30,298 to $58,249 in 2012 constant dollars between 1979 and 2012.Real earnings: ibid.849; the divergence is less extreme among women.Contribution to inequality: 844 with references, esp.Lemieux 2006.Causes:845–846, 849; for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ee also, e.g., Autor, Levy, and Murnane 2003; Acemoglu and Autor 2012.Innovation (proxied by patenting) and top 1 percent income sha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followed parallel tracks since the 1980s,which suggests that innovation-led growth boosts top incomes: Aghion et al.2016, esp.3 figs.1–2.Polarization: Goos and Manning 2007; Autor and Dorn 2013.Developing countries: Jaumotte, Lall, and Papageorgiou 2013: 300 fig.7.
[9] Education as solution: e.g., OECD 2011: 31; Autor 2014: 850.Flattened premiums: Autor 2014: 847–848.Europe: Crivellaro 2014, esp.37 fig.3, 39 fig.5; and see also Ohtake 2008:93 ( Japan); Lindert 2015: 17 (East Asia).Premiums across countries: Hanushek, Schwerdt,Wiederhold, and Woessman 2013.Mobility: Corak 2013: 87 fig.4, 89 fig.5.
[10] See now esp.Mishel, Shierholz, and Schmitt 2013.Mismatch: Slonimczyk 2013.For top incomes, see herein, pp.417–420.Cf.Mollick 2012: 128 for the notion that a general transition to a service economy may be raising inequality.
[11] Freeman 2009, Bourguignon 2015: 74–116, and Kanbur 2015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Earlier changes: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548.Country panel: Bergh and Nilsson 2010.Elites: 495; Medeiros and Ferreira de Souza 2015: 884–885.Global workforce: Freeman 2009: 577–579; Alvaredo and Gasparini 2015:748.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Jaumotte, Lall, and Papageorgiou 2013: 274.Trade competition: Machin 2008: 15–16; Kanbur 2015: 1853.Policies: Bourguignon 2015: 115;Kanbur 2015: 1877.
[12] Taxation: Hines and Summers 2009; Furceri and Karras 2011.Welfare: Bowles 2012a:73–100 (theory); Hines 2006 (practice).
[13]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ard 2009.Europe: Docquier, Ozden, and Peri 2014 (OECD);Edo and Toubal 2015 (France); and cf.also D’Amuri and Peri 2014 (Western Europe).For Latin America, see herein, chapter 13, p.368 n.1.Assortative mating: Schwartz 2010, with reference to earlier studies that attribute 17 percent to 51 percent of the overall increase to this factor.1980s:Larrimore 2014.
[14] Salverda and Checchi 2015 provid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is topic.For the importance of unionization and minimum wages, see 1653, 1657, and also, e.g., Koeniger,Leonardi, and Nunziata 2007; and see Autor, Manning, and Smith 2010; Crivellaro 2013: 12 for the role of minimum wages.Visser and Checchi 2009: 245–251 find that coverage and centralization of union bargaining rather than union density per se are critical variables in affecting inequality.Redistribution: Mahler 2010.Unions and premiums: Crivellaro 2013:3–4; Hanushek, Schwerdt, Wiederhold, and Woessman 2013.Variation between countries:Jaumotte and Osorio Buitron 2015: 26 fig.7.U.S.unionization rates and wage dispersion:Western and Rosenfeld 2011.U.S.unions and minimum wage: Jaumotte and Osorio Buitron 2015: 26, and, more generally, Salverda and Checchi 2015: 1595–1596.
[15] Tax rat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3: 7–9, esp.8 fig.4 for top income shares; Piketty 2014: 509.(But cf.Mollick 2012: 140–141.) Downward trends: 499 fig.14.1, 503 fig.14.2; 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61 fig.8.21(OECD); Scheve and Stasavage 2016: 101 fig.4.1 (inheritance taxes); Saez and Zucman 2016:Online Appendix, table B32 (U.S.); and see also herein, chapter 5, pp.143–144.Capital income: Hungerford 2013: 19–20.Sources of U.S.income and wealth dispersion: Kaymak and Poschke 2016: 1–25.Redistribution: OECD 2011: 37.Higher progressivity offset lower income taxes,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did not become more progressive, and benefits for those out of work contributed to market income inequality (38).
[16] I rely here on the excellent summary by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 2013, esp.104–105, 106 fig.1, 107, 108 fig.2, 109 fig.3, 110 fig.4, 112 fig.5, 118.See also Bartels 2008;Gilens 2012; Schlozman, Verba, and Brady 2012; Page, Bartels, and Seawright 2013.
[17] Distribution of income growth: Bivens and Mishel 2013: 58; Salverda and Checchi 2015: 1575 fig.18.11(b).Top 0.01 percent: WWID; including capital shares, those shares rose from about 2.4 percent in 1992 and 1994 to about .5.1 percent in 2012 and 2014; sixyear averages produce a steady rise, from 2.7 percent in 1992 and 1997 to 3.9 percent in 1996 and 2001, 4.6 percent in 2002 and 2007, and 4.8 percent in 2008 and 2014; moreover,the final two six-year means understate the scale of growth because they are depressed by the downturns centered on 2002 and 2009: the three-year means for 2005 and 2007 and 2012 and 2014 are 5.5 and 5.1 percent, respectively.Variation among countries: 1581 fig.18.16,1584 fig.18.17, 1592.Top 1 versus 2–10 percent: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496 fig.7.3, 497–498; and see 539 fig.7.20 for only a gentle decline of the top 2 percent to 5 percent wealth share over muc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662–663 stress that the rise in top incomes is a robust trend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better tax compliance.
[18] Keister 2014 and Keister and Lee 2014 offer recent surveys of the “1 percent.” Different types of explanations: Volscho and Kelly 2012; Keister 2014: 359–362;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57–562.Market forces or not: Blume and Durlauf 2015: 762–764.Firm size: Gabaix and Landier 2008; Gabaix, Landier, and Sauvagnat 2014.Cf.also Rubin and Segal 2015 for the sensitivity of top incomes to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Superstar/winner-takes-all models: Kaplan and Rauh 2010, esp.1046–1048; Kaplan and Rauh 2013; and cf.also Medeiros and Ferreira de Souza 2015: 876–877;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559–560.See also herein, 412 n.8, for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led growth on top incomes.
[19] Piketty 2014: 171–222, esp.171 fig.5.3, 181, 195; Piketty and Zucman 2015: 1311 figs.15.1–2, 1316 fig.15.6, 1317 fig.15.8.Housing: Bonnet, Bono, Chapelle, and Wasmer 2014;Rognlie 2015.Capital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s: Piketty 2014: 222 fig.6.5.Top income components: Morelli, Smeeding, and Thompson 2015: 676–679, esp.678 fig.8.27.Labor income is crucial for the “1 percent” of many countries: Medeiros and Ferreira de Souza 2015: 872.
[20] International variation: Roine and Waldenström 2015: 574–575 table 7.A2; Piketty and Zucman 2015: 1320–1326.With its extensive online datasets, Saez and Zucman 2016 effectively supersedes all prior studies of U.S.wealth distribution.For wealth shares, see ibid.Online Appendix table B1:顶层的1%群体财富份额从1978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39.5%,顶层的0.1%群体财富份额从1976年的6.9%上升到2012年的20.8%,顶层的0.01%群体财富份额从1978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11.2%。1929年,相应的份额分别为50.6%、24.8%和10.2%,这是美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前一个高峰。B21-B22:不包含资本收益的情况下,应税资本收入中的前1%份额从1978年的34%上升到2012年的62.9%,包含资本收益时则从36.1%上升到69.5%%。关于股利和利息收入的份额,见表B23a-b。
[21] Wealth Ginis: Keister 2014: 353 fig.2, 354.For the difficulties of measuring wealth shares,see, most recently, Kopczuk 2015, esp.50–51 figs.1–2.Association: 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and Saez 2013: 16–18.The share of wage income, including pensions, averaged 62 percent in 1979 to 1993, 61 percent in 1994 to 2003, and 56 percent in 2004 to 2013(WWID).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 argue that financialization has accounted for much of the decline in labor’s share of income.Investment income: Nau 2013, esp.452–454.Capital gains and dividends: Hungerford 2013: 19.
[22] Global wealth growth: Piketty 2014: 435 table 12.1.Offshore wealth: Zucman 2013 and esp.2015: 53 table 1.Cf.also Medeiros and Ferreira de Souza 2015: 885–886.
[23] Förster and Tóth 2015: 1804 fig.19.3 offer a succinct qualitative summary of the multiple causes of inequality and their contrasting effects.In addition to the ones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ey also note assortative mating, single-headed households, voter turnout, partisanship, and female employment.Levy and Temin 2007 offer a synthetic historical accou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World War II that first contained and later precipitated income inequality.Historically, the role of the stagflation of the 1970s, which provided a powerful impulse for disequaliz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lso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For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ee Massey 2007.
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看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的实际不平等程度大于只依靠标准度量方式衡量的不平等程度。第一,基尼系数这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最常用的概念,难以捕捉最高收入对于不平等的贡献的信息。弥补了这个缺陷的指数就会显示,整体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明显大得多。第二,如果把未报告的离岸资金纳入私人家庭财富的统计,这一类别的不平等程度也会显得更高。第三,我一直采取关注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指标的常规做法。然而,从绝对不平等指标(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来看,即使在西欧一些国家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一直不变或仅有一点上升,考虑经济增长后,这也意味着实际收入(以欧元或其他国家货币来衡量)的不平衡现象增加。
这种影响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公平同时增长率更强劲的的社会中更加强大,如美国等国家。即使在相对收入不平等情形最近有所减少以及经济增长强劲的拉丁美洲,绝对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世界范围内,绝对收入不平等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1988—2008年间,全球收入最高的1%的人得到的实际收入份额与世界第5、第6和第7个十分位数人口得到的份额差不多,但在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前者是后者的40倍左右。最后,正如我在附录中详细讨论的那样,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理论上的最大可能值随其人均GDP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即一个发达经济体比之前的农业经济体在系统上更加难以容忍极端资源错配时,我们并不清楚今天的美国是否比100或150年前的美国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更低。 [1]
最后一个警告确实只适用于名义上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现代经济体。毫无疑问,大部分欧洲大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可支配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有效不平等程度(可能的最大不平等程度实际发生的比例)比世界大战之前低得多。即便如此,尽管这些国家的高收入份额比美国的低,但支配家庭收入相对温和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再分配的结果,这种再分配抵消了普遍高水平的市场收入不平等。2011年,以再分配著称的5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典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74,这与美国的(0.465)和英国的(0.472)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的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0.274)远低于英国的(0.355)和美国的(0.372)。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上述5个国家略低一些,但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再分配的规模比美国更高(并且往往高很多),这表明那种欧元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典型的,更为平衡的最终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大范围的、强有力的政府平衡干预系统,这当然代价不菲。这种安排并不足以使欧洲未来永久保持平等。欧洲越来越多地区的社会和再分配公共支出已经很高。2014年,1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1/4~1/3,中央政府收取了44.1%~57.6%、中位数为50.9%的GDP。鉴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一财政收入比例难以再进一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欧盟、美国和OECD成员的社会支出占国民产出的比例都相当平稳,这表明它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足够高的水平。2009年,由于经济表现疲软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它的需求增加,它再次上涨,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新的高水平。 [2]
这些高均衡水平的福利系统如何承受两个日益增长的人口挑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欧洲人口老龄化。欧洲的生育率一直远低于维持人口不变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如此。到2050年,欧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将从39岁上升到49岁,工作年龄人口数量本来已经达到顶峰,从现在到那时可能会下降约20%。从现在到2050年或2060年,抚养比率——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的人口比例,将从0.28变为0.5或更高,80岁和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会从2005年的4.1%增加到2050年的11.4%。对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将相应增加,将会达到GDP的4.5%。这种年龄分布的根本性重构将伴随着相比过去几十年的、更低的经济增长率,预计2031—205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2%,2020—2060年为1.4%或1.5%,欧盟核心成员的数值比这些数值还低得多。 [3]
近几十年来,温和得多的老龄化速度未能对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可能会改变。从原理看,退休者与劳动者比例的缩减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同时伴随单亲家庭比例上升。私人养老金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这会趋向于维持或提高不平等程度。一项研究预测,由于老龄化,2060年德国的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高。在日本,外国籍出生人数占居民人数的比例远小于欧盟或美国的,其抚养率已经达到0.4,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考虑到日本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此前所采取的高度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曾有助于维持相对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分配。 [4]
所有这些预测都假定有大量的持续移民:如果没有这个人口因素的贡献,到2050年,欧洲赡养比可能高达0.6。因此,数以百万计的新来者将只能缓解长期老龄化进程的长期后果。与此同时,移民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再分配政策。在名为“第三次人口转型”的开创性研究中,基于对移民率和移民生育率的保守假设,杰出的人口学家戴维·科尔曼对7个国家的计算表明,到2050年,其中6个国家(奥地利、英格兰和威尔士、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外国籍人口占各该国家人口的比例(概念的定义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将达到1/4~1/3。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西欧人口的一半,其他许多国家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此外,这些移民人口在受教育儿童和年轻工人中占比更多——在某些国家,这个比例高达全国总人数的一半。预计非西方移民将占德国和荷兰人口的1/6。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假设这些移民趋势到21世纪中叶会有所减弱,到2100年,荷兰和瑞典可能会变成人口主要由外国籍出生人口构成的国家。 [5]
在农业文明出现后的这些地区的历史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不仅没有先例,而且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不平等状况。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们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是否能够与本地人成功融合。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现在远低于并将持续低于欧洲的国民,一些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妇女移民的就业率很低。这些问题的持续或恶化可能加剧这些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此外,第一代移民社区和新近移民家庭的增长拥有影响社会福利和再分配支出倾向和政策的潜力。阿达尔韦托·艾莱斯那和爱德华·格莱泽认为,福利政策与种族同质性具有相关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作为福利国家,其实现程度比欧洲更弱。他们预计,越来越多的移民将会降低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反移民情绪可能被用来废除再分配政策,并“最终推动这个大陆走向更为美国式的再分配水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测还没有得到实际发展的证实。最近的一项全面调查并未发现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证据——移民会损害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支持。 [6]
然而,更具体的观察表明,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更大的异质性和更多的移民实际上与更狭隘的社会政策条款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联系在一起。在欧洲的OECD成员中,种族多样性与公共社会支出水平之间可能只有微弱的负相关,但与受失业率影响的态度有更强的负相关性。如果许多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那么承担大部分财政负担的富裕的欧洲人对再分配所表达出的支持将更少。根据英国多项调查,如果因种族多样性导致穷人被认为是异类,那么社会对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倾向就会减弱。异质性的来源和维度至关重要:移民和宗教异质性比少数民族种族的存在对国家福利条款的不利影响更严重。这些因素中的前两个已经成为欧洲经验的特征,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持续移民压力将确保它们的持续性且可论证相关性增强。对于所有这一切,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欧洲自身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和移民的背景下,将改变目前国家人口构成的欧洲“第三次人口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下一代人的生活中,它可能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改变既有的再分配和不平等模式。考虑到当前系统的高成本,以及由老龄化、移民和日益增长的异质性带来的不平等压力,这些变化更有可能引起不平等程度提高而不是抑制它。 [7]
不是所有人口因素都可能对不平等的进一步演变产生重大影响。无确定性证据表明,可能扩大美国家庭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门当户对的婚配率近年来在不断上升。同样,收入方面的代际流动似乎并没有放缓,虽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框架做出确切的结论。相反,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可能对长期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更大。只要邻居的收入间接影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定收入群体的空间集中度扭曲了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物品的分布,那么人口分布中日益增加的经济失衡将持续下去——而且确实加强了未来世代的不平等。 [8]
皮凯蒂认为,因为资本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持续的资本积累将提高资本所有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及其对国民收入的整体重要性,从而推动不平等程度继续加大。这种观点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迫使其主要支持者强调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但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其他经济和技术力量比比皆是。已经被确认的、在发达国家具有加剧不平等效应的全球化,在不久的将来也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全球化的过程是否会创造出一群不受国家政策限制的全球超级精英还有待观察,如被大众媒体追捧、广受诟病的“达沃斯达人”。自动化和电脑化由于其更加开放的本质,必将影响劳动回报的分布。据一项估计,在全美劳动市场702个职业中,几乎一半的就业岗位都面临由计算机化带来的风险。尽管现有预测认为,自动化不会无限度地使劳动市场两极化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但未来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突破将使机器能够赶上或超越一般人类智力,任何预测长期结果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9]
我们对人体的重塑将为不平等的演变开辟新的领域。生控体系统和基因工程拥有扩大个人甚至其后裔间不平等的潜力,远超他们的自然禀赋和能控制的体外资源,他们也许会这么做来反哺未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由于纳米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展了人造植入物的使用程度和效用,其应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局限于功能恢复,而是转向功能增强。在过去几年中,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能凭借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方式在培养皿和存活生物体中删除和插入特定的DNA片段。虽然这种干预措施的后果可能仅限于单个生物体,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操纵精子、卵子和小胚胎的遗传构成来制造遗传物质。第一个修改(非存活)人类胚胎基因组的实验结果于2015年发表。近期这一领域的进展非常快,将使我们继续深入未知的领域。根据成本和可得性,富人可能会享受到这些生物技术和基因改良的特权。
政治限制可能不足以压制这些机会:与公共卫生不同,生物增强是一种升级,因此更容易产生不平等分配的结果。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限制已经被提出,这很可能会导致更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将使那些有能力在这些国家享受私人待遇的人获得优势——最有可能在亚洲部分地区。从长远来看,为富有和拥有良好联系的人创造设计婴儿,可能会削减“基因富人”和“基因穷人”之间的流动性,至少在理论上,最终会分叉成不同的物种——如“基因富人”“自然人”或其他任何人,普林斯顿的遗传学家李·希尔弗就是这样设想的。 [10]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未能有效应对技术变革。这种状况在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中可能不会改变,除非计算机化的突破达到一个临界点。但是,在人类由于基因工程或身体–机器结合(很有可能这两种情况都有)而变得更加不平等后,这种范式将会发展到一个突破点。教育是否能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工身心增强技术呢?我们还是不要过于担心这些有关未来的事情吧!在人们开始担心如超人一样的超级机器人以前,世界就面临着有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更为普通的挑战。我现在最后一次回到这本书的中心话题:减少不平等。那么,矫正不平等的前景如何呢?
目前并不缺乏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已经开始加入雕琢更少但更受欢迎的畅销书同行和各种记者的行列,他们出版著作,列出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措施的长长清单。这可是个获利丰厚的行业。税收改革占突出地位。(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是就美国而谈的。)收入应该以更累进的方式征税;资本收益应如普通收入一样课税,并且一般而言应该课更高的税率;累退工资税制度应该被废除。应该直接对财富课税,课税的方式应该足以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诸如贸易关税和创建全球财富登记制度等措施将有助于防止离岸逃税。应对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结束对它们的隐性补贴。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建议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从源头征税。此外,更大的对资本的一次性课税将减少公共债务,重新平衡私人与公共财富的比例。前面提到的对技能的需求与供给方法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作用的关注。公共政策应能通过平等的教育准入和教育质量促进代际流动。将学校资金与地方财产税脱钩将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普遍提供学前教育是有帮助的,可以对高等教育进行价格管制。更普遍的是,改善教育将使身处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的劳动力“加强技能”。
在支出方面,公共政策应提供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各种保险(从住房价值到工人拥有的合作社,再到人们健康的资产价值)免受外生冲击。普遍的卫生保健将缓冲这些冲击。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的创业活动应该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融资,破产法应该对债务人更加宽容。贷款者应该得到激励或应该获得重组抵押贷款的机会。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下。设立基本的最低收入;把补助金与个人储蓄挂钩,直到其达到一个上限;为每个孩子提供最低数量的股票和债券。企业管制是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设立能够调整市场收入分配的专利法、反托拉斯法和相关合同法;抑制垄断;更严厉地管制金融部门。企业所得税应与CEO薪酬对工人工资中位数的比率相挂钩。高管寻租行为应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来解决。股东和雇员的地位应该通过确保后者的代表权和投票权以及迫使公司与工人分享利润的方式来维持。制度改革应该重振工会力量,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并创建联邦就业项目。移民政策应该鼓励熟练劳动力的引入,以降低技能溢价。全球化的不均衡影响可以通过协调国际劳工标准,对来自外国的收入和利润无论生产地点的进行征税来减轻。应该管制国际资本流动——根据一项特别大胆的建议,美国可能要求贸易伙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各自工资中位数一半的水平。在政治领域,美国应该通过竞选资金改革来消除不平等,并采取措施提高选民投票率。干预媒体以使它们的报道更加符合民主化原则。 [11]
最近的讨论主要(甚或排他地)集中在政策措施的内容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其成本和收益的可能规模,以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可行性。举几个例子就够了。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估计,为了使美国1%的可支配家庭收入的份额降低到哪怕是1979年的水平,对他们征收的有效税率将不得不翻番,从35%变为67.5%。这一目标“从政治观点来看,并不完全可行”。皮凯蒂认为,综合考虑经济成本与平等利益,最高收入者的“最佳”所得税税率应该为80%,但他又坦然承认,“在短期内任何此类政策被采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有效的全球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建议将全球政策协调的门槛提高到令人目眩的高度。拉维·坎伯提倡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协调劳动标准——类似于对抗全球化压力的奇迹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机构的政治可行性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放在一边”。皮凯蒂明确宣称,这项提议中的“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但他又认为在欧洲范围内征收财富税“没有技术原因”的阻碍。这类崇高的想法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无益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更切实可行的措施上转移走了。所有这一切建议,都缺少对有关调动政治上的大多数以执行这些建议所需要的手段的严肃思考,这太明显了。 [12]
安东尼·阿特金森近期提出的关于如何减少英国不平等的蓝图,是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阐明了这些政策导向方法的局限性。众多雄心勃勃的措施构成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公共部门应通过“鼓励增雇工人的创新”来影响技术变革;立法者要努力“减少消费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恢复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公司应以“反映道德原则”的方式来与工人分享利润,或被禁止为公共机构提供物品或服务;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应提高至65%,对资本收入的课税应比对劳动所得课税更重,对地产和赠予的征税应在所有者生前加强,房产税应根据最新的评估来设定;国民储蓄债券应担保得到一个“正的(可能是补贴的)实际利率”直到达到个人的上限;法定最低工资应“设定在生活工资水平上”;每个公民在储蓄债券到期或之后应获得一份资本捐赠;“政府应该以生活工资水平向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就业”(阿特金森自己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切实际”)。可能的附加措施包括年度财富税和“以总财富为基础的个体纳税人全球税收制度”。此外,应说服欧盟引入“儿童普遍基本收入保障”,将其作为一项应税福利,与国家收入中位数挂钩。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是否可以真正实现的时候,阿特金森重点关注其对经济施加的成本(这点至今尚不清楚);对抗全球化的压力(对此,他希望通过欧洲或全球政策协调来进行);财政负担能力。与其他平等改革措施的支持者不同,阿特金森还对这一方案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估计:如果实施了4项主要政策,即更高和更累进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折扣,为每个孩子支付大量的应税福利,保证所有公民的最低收入,那么平等化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下降5.5个百分点,这可将目前英国和瑞典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缩小一半多一点。更有限的不平等变化将会使基尼系数减少3个或4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2013年,英国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因此,即使是几个相当激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组合,也只能部分地扭转不平等复苏的影响,更温和的政策产生的好处更小。 [13]
“这一切是他的乌托邦?” [14] 即使它们不是完全的乌托邦,许多政策建议中都缺乏历史意识。边缘的改革不太可能对当前市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势产生重要影响。阿特金森的讨论有一个独特优点:它既考虑一套雄心勃勃的措施的成本,也考虑该措施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可能影响。而对任何一项现实的政策配置来说,其好处相对不大。更普遍的是,人们似乎对如何将这些建议变为现实,甚至对它们是否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兴趣。然而,关于矫正,历史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激进的政策干预通常发生在危机时期。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措施主要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换成不同情况它们可能就是不可行的——至少,不能在规模上等同。第二个教训更加直截了当:政策制定只能有一定效果。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社会内部物质不平衡的压迫是由暴力驱动的,这种力量在人类的控制以外,远超现在任何可行的政治议程范围。在当今世界,那些最有效的矫正机制都无法运作:“四骑士”已经跳下了他们的战马。没有正常人愿意让他们再次上马。
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一直延续至今。军事冲突的形式一直由技术决定。有时,向古代战车或中世纪骑士那样的高价值资产投资是有利的,有时,向大规模的步兵那样的低价值资产投资也会获得优势。在西方近代早期,财政–军事国家成熟,国家的大规模军队取代了雇佣军。在法国大革命中,军事动员率达到新高,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动员达到数百万人的顶峰。从那以后,军队发展趋势又一次从重视数量转向了重视质量。理论上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核武器就可使大规模常规战争过时,但在实践中,常规战争在低风险冲突中,在缺乏核能力的两个国家之间,或在涉及无核能力的国家的冲突中依然存在。征兵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被能够处理更复杂设备的专业志愿军队取代。
在那些仍从事军事行动的相对较少的发达国家中,军事行动往往脱离主流社会,平等化的“动员效应”也消失了。在美国,1950年是最后一个未经严肃辩论就通过增税支付战争费用法案的年份。即使这个法案依然有效,1964年的《税收法案》依然成为1981年之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这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在扩大。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费开支的激增以及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都伴随着减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逆转了世界大战期间的趋势。1982年福克兰战争前后的英国也是如此。
虽然近期的冲突规模相对较小,“冷战”也从未真正发展为公开的敌对行动,但即使爆发更大的战争,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改变这一轨迹。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可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只要这个战争是没有原子武器的常规战争,很难想象它们会动员很大的军队参战。早在70多年前,太平洋战争主要使用的是昂贵船只和空中力量,而不是步兵部队,未来这个地区的任何战斗将主要涉及空中和海上力量、导弹、卫星和各种网络战,其中没有一个适合大规模动员。再极端的也不会是核战争。目前,俄罗斯正在取消义务兵制、更多采用志愿兵制,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征兵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大型战争的潜在敌手,都采用志愿兵制。即使军事能力远超其日益不稳定的邻国的以色列,也正在设想从义务兵制变为志愿兵制。
从根本上看,在21世纪的战场上,人们不清楚庞大的步兵部队最终能够实现什么。目前对未来战斗性质的预测聚焦在“机器人、智能弹药、无处不在的传感和极端网络,以及网络战的潜在巨大影响”。未来将会有更少但更专业的人类战斗人员,他们配备了外骨骼、植入物,最终可能增强基因,用这些手段加强他们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他们将与各种形状、大小的机器人共同作战。这些机器人有的像昆虫一样小,有的像车辆一样大,有的可能会操控诸如激光和微波射线这样的定向能量武器以及力场。小型武器将精确定位到特定个人,因此将取代那些定位能力不够的火力投射,并且高速高空超级无人机可能使人类飞行员变得多余。这些场景与早期工业化下的战争形式相去甚远,将进一步加强军队与民用领域的分离。这种冲突对平等化的影响可能会集中在金融市场,触发类似于最近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那种错位,而且,它只会在几年后的反弹前暂时削减精英财富。 [15]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涉及有限的战术、使用小规模核装置的战争。只有全面的热核战争才可能重置现有的资源分配。如果战争升级仍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公共机构仍然运转,而足够数量的关键基础设施未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和军事部门将冻结工资、价格和租金;阻止非必需的银行提款;实行食品综合配给制;强征所需商品;采取各种形式的中央计划,包括集中配置稀缺资源以支持战争、政府行动和生产对生存至关重要的生存物品;分配住房;甚至可能诉诸强迫劳动。在美国规划的“战后”计划中,让整个经济分担战争损失一直是一个关键政策目标。大国之间的任何战略层面的核弹头攻击,都将大规模地摧毁物质资本,破坏金融市场。最有可能的结果不仅是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将使现有资源再平衡,以及发生权力从资本到劳动力的转变。
不受限制的核战争导致的世界末日局面势必把矫正的效果推到所有上述预期结果之外。它是系统崩溃的极端版本,其严重性甚至超过第9章讨论的早期文明的戏剧性衰落。尽管描述劫后世界的那些当代科幻小说有时设想了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人和被剥夺的大多数人之间的高度不平等,但现代史前的那种彻底贫穷和分层较少的崩溃后社会的经验可能更接近未来“核冬天”的真正情形,但“核冬天”不大可能发生。尽管核扩散可能会改变全球某些区域范围内的规则,但在20世纪50年代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的那个既有风险仍然会发挥相同作用。此外,仅仅是库存的大量核武器就使得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地区不太会大规模地参与常规战争,同时,它又会将冲突置于全球的边缘地区,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严重损害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可能性。 [16]
武器技术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变得更加爱好和平的可能性。回溯到石器时代的各种证据强烈地表明,从长期的历史中看,一个人因暴力事件死亡的平均概率一直在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至今未变。虽然这种长期的转变似乎是由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和随之而来的文化适应驱动的,但是已经提到的一个更具体的因素将会加强我们这个物种的和平化倾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西方已经开始的、最终会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会在整体上降低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这对于评估美国与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尤为重要,它们中许多都面临着从年龄较小的群体向老年群体的剧烈人口转型。所有这一切都支持米拉诺维奇的希望:“人类今天面对一个和一百年前时非常类似的情形,将不会允许用一场世界大战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17]
接下来的两个世界末日骑士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甚至比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更过时。正如我在第8章中所表明的那样,仅仅依靠起义是很少成功的,通常不能实现实际上的平等。一些革命能够大大地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衡。然而,1917—1950年间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大规模扩张根植于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再次上演。随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以失败告终前,只零星地在古巴、埃塞俄比亚、南也门,以及最重要的是在1975年前的东南亚取得了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进行了温和的政权变更,证明了这些政权变革要么短暂,要么在政治上太温和。秘鲁的共产主义起义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被镇压。市场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其他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根基。即使古巴和朝鲜也未能摆脱这种全球趋势。在这个时候,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没有更激进的左派革命,也没有任何具有类似潜力的暴力平权运动出现。 [18]
如第9章讨论的那种国家衰败和制度崩溃同样变得极其罕见。最近的国家衰败事件往往局限于中非和东非以及中东周边地区。2014年,系统和平中心的国家脆弱指数把最低评分给了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除了缅甸以外,17个脆弱的国家也位于非洲或中东。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明,即使是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也绝不能幸免于分裂的压力,当代发达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太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财政扩张,高收入国家的国家机构通常在社会上极为强大和根深蒂固,使得政府结构的大规模崩溃和大矫正不可能同时发生。即使在最弱势的社会中,国家的失败往往与内战有关,这种内战通常不会产生平等化的结果。 [19]
这给我们留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骑士:严重的流行病。新的和潜在的灾难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万万不能忽视。由于人口增长和热带国家的森林砍伐情况,疫病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感染情况正在变得多见。食用丛林肉也维持了这一传播链,工业畜牧养殖使微生物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病原体武器化和生物恐怖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经济发展和全球互联有助于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监测和应对这些威胁。快速的DNA测序,在野外使用更为方便的实验室设备小型化,通过建立控制中心和利用数字资源来追踪疫情的能力是我们武器库中的强大武器。
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点,与第10章和第11章所讨论的前现代流行病的相对规模接近的任何事物都会导致世界上数亿人死亡,这远远超过最悲观的估计。此外,全球未来的任何疫病流行都可能主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治疗干预措施几乎没有什么用,1918—1920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率受人均收入水平的严重影响。今天,因为医疗干预将减少严重疾病暴发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死亡率将更低。从2004年“西班牙流感”报告的死亡率推断,全球预计5000万~8000万的死亡病例中的96%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复杂的武器化可能会使一个更强大的超级细菌产生,但释放这样一个细菌几乎不符合任何国家层面的行为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生物恐怖主义可能只有很小的成功机会,更不可能真正导致全国或更广范围内的人口死亡。
第二点涉及未来流行病对经济分配产生的后果。很难想象今天世界的传染病引起的突然的灾难性死亡会像农业时代那样铲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我们甚至不知道导致5000万~1亿人或3%~5%的世界人口丧生的1918—1920年全球流感对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一战”产生了平等化影响。尽管现在一般性感染(如流感)会更严重地影响到穷人,但当整个经济基本保持不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推测,穷人阶层的死亡危机将会推高低技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一个当代的流行病真的成为灾难,即夺走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生命,那它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被遏制的,并且国界和社会经济范围也无法阻止它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它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代经济体及其高度差异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与劳动力供应和资本存量估值相关的平等化效应。即使在一体化程度极低的农业社会中,瘟疫引发短期混乱后,富人的状况也不会比穷人好多少。从长远来看,分配后果将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新方法塑造:在被瘟疫耗尽的经济中,机器人最终可能代替许多工人。 [20]
我们不能断定,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暴力冲击在未来将不会出现。无论规模多么小,一场大的战争或一个新的黑死病可能粉碎已建立的秩序,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出最经济的预测:四个传统的矫正力量目前已经消失了,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出现。这使人们对未来平等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历史的结果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矫正分配的历史也不例外:制度安排在决定压缩冲击的分配后果中是至关重要的。统治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强制权力的变化使得瘟疫提高了一些社会中的实际工资,但其他社会的不会;世界大战使一些经济体的市场收入分配扁平化,却在其他经济体中促使雄心勃勃的再分配制度出现。
但是,每一个已知的大矫正时期背后,总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为什么约翰·洛克菲勒实际上比一代和二代后最富有的同胞富裕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唐顿庄园》描述的英国被一个以全民免费医疗和强大工会闻名的社会取代,为什么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第三季度的贫富差距比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小得多——事实上,为什么100代人之前的古代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已拥抱平等的理想,力求将其付诸实践,这些背后都有一个重大原因。为什么在3000年以前埃及低地地区的高大、强壮的埃及人不得不仅用旧衣服裹着埋葬了他们死去的同伴,或者仅仅使用粗制滥造的棺材处理尸体;为什么罗马贵族的后代为了得到教皇的赏赐物而排队,为什么玛雅酋长继承人与普通大众吃一样的食物;为什么拜占庭和埃及的农民、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木匠,以及现代早期墨西哥的雇佣工人比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同龄人都赚得更多、吃得更好,这些背后也有一个重大原因。这些重大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共有一个基本特征:对既定秩序的大规模的暴力破坏。有史以来,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改朝换代的革命、国家衰败和流行病引起的对不平等的周期性压缩,总是使任何已知的完全和平的平等化手段相形见绌。
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也许现代化是真的不同。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会使我们走向这样一个奇点:所有人融合成一个全球互联的、人体和机械合二为一的超有机体,无须再担心不平等。或者技术进步可能将一个被生物、机械、电子技术和基因强化的精英从普通人类中分离出来,将不平等推向新的极端,而后者永远被他们的霸主所拥有的更优越的能力压在谷底。或者上述两者都不是,出现我们无法构想的结果。然而科幻小说只能带我们想象到这里。我们暂时停留在我们所拥有的心灵和身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制度之中。这表明矫正的未来前景渺茫。对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保持和调整精心制定的高税收和广泛的再分配制度,或对亚洲最富有的民主国家而言,保留其非常公平的税前收入分配以遏制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而增加了动能。它们能否坚持到底是值得怀疑的:不平等在各地都在不断加剧,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否定现状的趋势。如果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越来越难实现,那么任何使它们更平等的企图一定面临更大的障碍。
几千年来,历史在不断上升的、稳定的不平等和暴力压缩之间交替着。从1914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十年里,世界上的富裕经济体和共产主义政权都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矫正过程。从那时起,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一个可能会长期存在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收入集中的回归。当未来变成历史,人们可能发现,和平政策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应对今后日益增长的挑战。然而,有其他选择吗?我们所有珍视经济平等的人都应该记住,它在巨大的悲痛中才会出现,例外情况很罕见。对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抱着一个慎重的态度。
[1] See herein, chapter 15, pp.409–410 (Gini adjustments), 422 (offshore wealth), Introduction,p.13 (absolute inequality); Hardoon, Ayele, and Fuentes-Nieva 2016: 10 fig.2 (growing absolut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top 10 percent and the bottom half in Brazil 1988 to 2011).For global inequality, see Milanovic 2016: 11 fig.1.1, 25 fig.1.2: real incomes of the global 1 percent rose about two-thirds, comparable to rates of the order of 60 percent to 75 percent between the fortieth and seventieth percentiles of the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yet 19 percent of the total gain went to the 1 percent, 25 percent to the next highest 4 centiles, and only 14 percent to those in the middling three deciles.For even larger absolute gains of the global 1 percent relative to the bottom 10 percent, see Hardoon, Ayele, and Fuentes-Nieva 2016: 10–11.Effective inequality: herein, appendix, pp.452–455.
[2] Ginis: SWIID.In 2011 Portugal had an even higher market income Gini (0.502) than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countries with lower market Ginis include Austria,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pain, and Switzerland, although Belgium is the only real outlier: see herein, chapter 15, p.406 table 15.1.In this latter group, only in Belgium and Spain was the gap between market and disposable income Ginis smaller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For the redistributive effort required to stem rising market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see herein,chapter 15, pp.406–407.Social spending: OECD 2014: 1 fig.1 (in descending order, France,Finland, Belgium, Denmark, Italy, Austria, Sweden, Spain, Germany, Portugal, and, a smidgen under 25 percent, the Netherlands).Central government share in GDP: OECD,General government spending (indicator), doi: 10.1787/a31cbd4d-en.Bergh and Henrekson 2011 survey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hare of GD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igh-income countries.Social spending trends: OECD 2014: 2 fig.2.For the main components, see 4 fig.4.
[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2013, and 2015 are key reports on the scale and consequences of aging in Europe.Cf.also briefly United Nations 2015 for global trends.Fertility rates: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12 (about 1.5 now, projected to rise to about 1.6 by 2050).Median age and working age population: 13.Dependency ratios: 13 (rise to 53 percent by 205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rise to 51 percent by 2050) and 2015: 1 (rise to 50.1 percent by 2060).Eighty-year-olds and older: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13.Cf.46 fig.2.7., 49 fig.2.9, and Hossmann et al.2008: 8 on the range of future age pyramids.Growth as share of GDP: 13, with 70 table 3.3 (health care), 72 table 3.4 (long-term care); but contras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4, for an additional 1.8 percent of GDP in spending required by 2060, albeit with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4–5).Economic growth rate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62 (1.3 percent for EU-15 and 0.9 percent for EU-10 in 2031–2050), 2013: 10 (1.2 percent 2031–2050), 2015: 3 (1.4–1.5 percent 2020–2060).
[4] Effects on inequality: Faik 2012, esp.20–23 for the forecast (Germany);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10–11, 16.Japan: Ohtake 2008: 91–93 for the disequalizing consequences of ag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n expansion of informal labor relations among the young.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and domestic equality: Lindert 2015: 18.
[5] Dependency ratio: Lutz and Scherbov 2007: 11 fig.5.Coleman 2006, esp.401, 414–416.Even a zero immigration policy would reduce the foreign-origin population by not more than a third to a half by 2050 (417).Children and young worker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27.
[6] Scale of replacement: Coleman 2006: 419–421.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integration: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15, 2013: 28.Heterogeneity: Alesina and Glaeser 2004: 133–181 (quote: 175).Survey: Brady and Finnigan 2014: 19–23.
[7] Waglé 2013 is now the most detailed analysis, noting throughout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ity and welfare (esp.263–275).Ho 2013 argues that ethnic diversity per se does not reduce redistribution once other identiti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See Huber, Ogorzalek, and Gore 2012 for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emocracy on inequality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countries, and Lindqvist and Östling 2013 for a model that predicts maximization of welfare under ethnic homogeneity.Correlations: Mau and Burkhardt 2009; Waglé 2013: 103–262.Attitudes: Finseraas 2012; Duch and Rueda 2014;and see also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15, 104.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heterogeneity:Waglé 2013: 164, 166.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246 speculate that future immigration might raise European inequality by increasing the labor supply.
[8] Greenwood, Guner, Kocharkov, and Santos 2014 find that assortative mating increas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but not since, whereas Eika, Mogstad, and Zafar 2014 observe its decline among the college-educated and its rise at low education levels.Fo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see herein, in the introduction, p.20, and esp.Chetty et al.2014 for stable rates.Residential segregation: Reardon and Bischof f 2011a: 1093, 1140–1141; 2011b: 4–6.
[9] Piketty 2014: 195–196; Piketty and Saez 2014: 840–842; Piketty and Zucman 2015: 1342–1365, esp.1348 fig.15.24.For a random sample of critiques, see Blume and Durlauf 2015:755–760 and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5, the latter with the response by Piketty 2015b:76–77, who notes the uncertainties involved in his prediction (82, 84).Cf.also Piketty 2015a for responses to other work.For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see herein, chapter 15, pp.413–414.Disequalizing trade competition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is likely to continue: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6: 250; cf.Milanovic 2016: 115.Global super-elite: Rothkopf 2008; Freeland 2012.On computerization and labor markets, see now esp.Autor 2015:22–28, and, more generally, Ford 2015.Estimate: Frey and Osborne 2013.Among many others,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4 stress the enormous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computerization.For AI, see most recently Bostrom 2014.
[10] Center for Genetics and Society 2015 surveys recent advances in genetic techniques,most notably genomic editing by means of CRISPR/Cas9; see esp.20–25 on germline modification, and 27–28 on ethics and inequality.Liang et al.2015 report on human embryo gene editing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which was largely unsuccessful.See also Church and Regis 2014 for the potential of synthetic biology.Harari 2015 makes valuable points about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Bostrom 2003 considers the equality outcomes of genetic modifications, while Harris 2010 is sanguine about their ethics and desirability.Speciation: Silver 1997.
[11] This is a florilegium of the ideas put forward in OECD 2011: 40–41; Bowles 2012a: 72,98–99, 157, 161; Noah 2012: 179–195; Bivens and Mishel 2013: 73–74; Corak 2013: 95–97;Stiglitz 2013: 336–363; Piketty 2014: 515–539, 542–544; Blume and Durlauf 2015: 766;Bourguignon 2015: 160–161, 167–175; Collins and Hoxie 2015: 9–15; Kanbur 2015: 1873–1876; Ales, Kurnaz, and Sleet 2015; Reich 2015: 183–217; Zucman 2015: 75–101.
[12] Income tax: Bourguignon 2015: 163; Piketty 2014: 512–513 (quote: 513), drawing on Piketty, Saez, and Stantcheva 2013.Global labor standards: Kanbur 2015: 1876.Wealth tax:Piketty 2014: 515, 530 (quotes; my emphasis).Criticism: Piachaud 2014: 703, on the idea of a global wealth; cf.also Blume and Durlauf 2015: 765.Others have criticized Piketty’s focus on taxation: 765–766; Auerbach and Hassett 2015: 39–40.Bowles 2012a: 156–157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devising politically viable policy designs.Regarding political action, Levy and Temin 2007: 41 note that “[o]nly a reorient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can restore the general prosperity of the postwar boom,” and Atkinson 2015: 305 reminds us that “[t]here has to be an appetite for action, and this requires political leadership.” This begs the question of implementation; Atkinson’s reference to the improvements made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subsequent postwar decades” (308; cf.55–77 for a historical survey) is very much to the point but offers scant hope for the present.Stiglitz 2013: 359–361, on the prospects of putting his numerous proposals into practice, offers no substantive suggestions.Milanovic 2016: 112–117 voices healthy skepticism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of various equalizing forces (political change, education, and an abatement of globalization pressures), placing hope on the slow dissipation of rents over time and the emergence of future technologies that might increase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lowskilled workers.He is particularly pessimistic about the short-term prospects of economic equ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ll indicators point to a continuing rise in inequality in the near future (181–190, esp.190).
[13] Atkinson 2014a and 2015.In addition to Atkinson 2015: 237–238, I quote mostly from the summary version (2014a).For the question “Can it be done?” see 241–299.Gini reduction:294, with 19 fig.1.2, 22 fig.1.3 (and cf.also 299 for a probable reduction of about 4 points).The British income Gini fell by about 7 points during World War II: 19 fig.1.2.
[14] Piketty 2013: 921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iketty 2014: 561).
[15] Projections: Kott et al.2015, esp.1 (quote), 7–11, 16–17, 19–21.For the future use of robots, see also Singer 2009.For the effects of recent economic crises, see herein, chapter 12, p.364.
[16] See Zuckerman 1984: 2–5, 8–11, 236–237, 283–288 for U.S.government planning for the aftermath of a nuclear war.Forced labor: the U.S.Oath of Allegiance requires that citizens“perform work of national importance under civilian direction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See Bracken 2012 on new forms of nuclear conflict nd Barrett, Baum, and Hostetler 2013 on the odds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2015: 4 assesses the probability of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major power “to be low but growing,” and predicts that its “consequences would be immense.” For the displacement effect, see international tudies scholar Artyom Lukin’s contribution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rtyom-lukin/world-war -iii_b_5646641.html.Allison 2014 provides an accessible survey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1914 and 2014.Morris 2014:353–393 considers a range of future outcomes.
[17] Declining violence: Pinker 2011; Morris 2014, esp.332–340.See Thayer 2009 for a surve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y and war, and Sheen 2013 for the irenic effects of future aging in Northeast Asia.Quote: Milanovic 2016: 102–103.
[18] 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是一个有着公平收入记录的左翼运动,通过议会制度继续工作,一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阻力,可能无法在其对经济的不善管理中幸存下来。
[19] Index: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SFImatrix2014c.pdf.For civil war and inequality, see herein, chapter 6, pp.202–207.I discuss the state failure in Somalia in chapter 9, pp.283–286.
[20]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popular science books describing the emergence of novel infections and considering future threats: see, most recently, Drexler 2009 and Quammen 2013.The bestinformed contribution has been made by Stanford-affiliated virologist Nathan Wolfe, who stresses our improved capabilities to monitor and respond: Wolfe 2011.Scale: for what it is worth, Bill Gates reckoning with tens of millions of future deaths: https://www.ted.com/talks/bill_gates_the_next_disaster_we_re_not_ready?language=en.Extrapolation from “Spanish flu”:Murray et al.2006.Bioterrorism: e.g., Stratfor 2013.For pathogens with weaponization potential,see Zubay et al.2005.
不平等程度能够上升到多高?重要的一点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给定一个人口群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没有极限的。理论上,一个人能够拥有一切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同时其他人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劳动收入或者财富转移来维持生存。这种分配将会产生一个无限接近于1的基尼系数或一个最高为100%的财富份额。从纯粹的数学角度看,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有可能从0(代表完全平等)上升到接近于1(代表完全不平等)。然而,无限接近于1的基尼系数在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最低额度的收入才能存活。为了解释这一基本需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提出了“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概念,用来衡量在给定平均人均产出水平下,理论上可能的最高不平等程度。人均GDP越低,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均剩余就越少,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就会越受限制。
设想一个平均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收入基尼系数必然为0,因为即使很小的收入差距都会迫使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的收入下降到最低生存保障以下。尽管这是完全可能的(一些人会变得更加富裕而另一些人会忍饥挨饿),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口将会逐渐萎缩。如果平均人均GDP略高于最低生活标准,假设在一个100人的群体中,平均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那么,其中的某一个人可以要求得到最低生活标准6倍的收入,而其他人都维持在最低生活标准。这时的基尼系数为0.047,收入最高的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为5.7%。假设平均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两倍(对现实生活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占有全部可获得的经济剩余,那么,这个唯一的最高收入者将获得所有收入的50.5%,这时基尼系数就会达到0.495。因此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在平均人均产出水平为最低生活标准的5倍时,基尼系数将最可能接近0.8(图A.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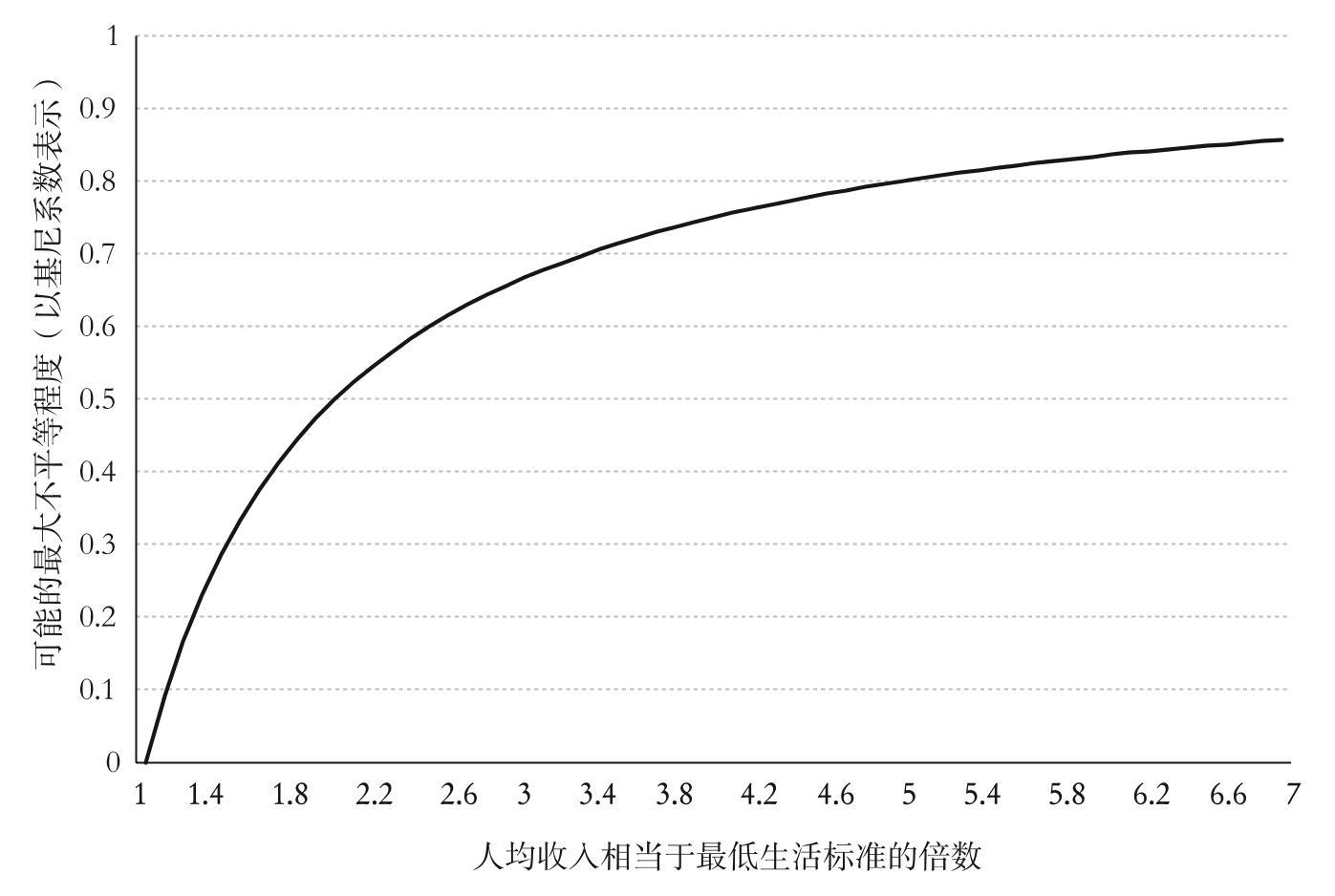
图A.1 不平等可能性曲线
图A.1表明,在人均GDP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时,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变化最大。一旦人均GDP增加到最低生活标准的数倍后——这是现代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就会上升到0.9的高水平,并达到无限接近于1的理论上限。因此,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主要有助于我们理解前现代社会和当代低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最低生活标准定义为年收入300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尽管年收入稍高一些可能会更可信,但这是一个传统指标,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不平等潜力的调整给年人均GDP 1500美元的经济体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前现代经济体都在这一范围内,这意味着图A.1所描绘的范围涵盖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在国家层面上,16世纪初的荷兰最先达到300美元的生存水平的5倍,英国大约是在1700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美国是在1830年,法国和德国是在19世纪中叶,日本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而中国整体上直到1985年才达到这一水平,印度则是在1995年以后。 [2]
用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最大值除以观测到的收入基尼系数就得到了榨取率,它衡量了收入高于最低生存保障的人理论上可能榨取的不平等的比例。榨取率可能从完全平等条件下的0变化到100%,此时某一个人获得了全部产出中人均最低生存收入总和之外的部分。观测到的基尼系数和不平等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越小,榨取率就越接近于100%。米拉诺维奇、林德特和威廉森利用提供了收入分配原始指标的社会表格(这种表格的样式可以追溯到格雷戈里·金为1688年的英格兰制作的著名的社会表,它区分了从勋爵到贫民之间的33个阶级),与可获得的人口普查资料相结合,计算了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的28个前现代社会的榨取率(图A.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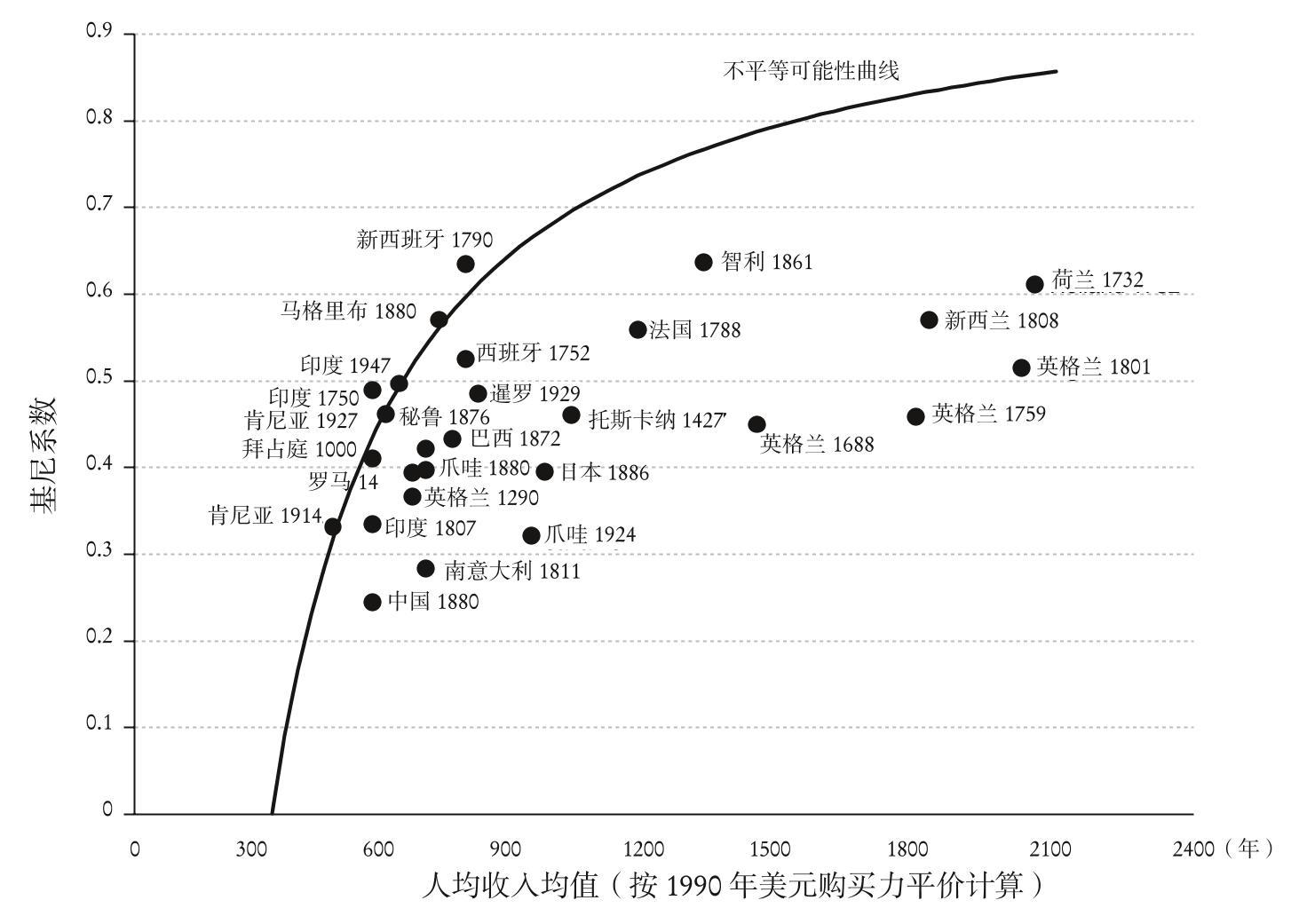
图A.2 前工业社会的收入基尼系数和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估计
这28个前现代社会的平均收入基尼系数大约是0.45,平均榨取率为77%。相对于较发达社会,较贫穷社会往往更接近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样本中,21个平均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的社会的平均榨取率为76%,与其他7个平均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之间的社会78%的平均榨取率几乎一样。只有当经济绩效提高到人均产出为最低生活标准的4~5倍时,平均榨取率才会下降:英国和荷兰在1732—1808年之间的平均榨取率为61%。样本中最高的5个榨取率,处于97%~113%的区间内,很可能是数据不充足下的非真实数据,尤其是对那些基尼系数显著超过了其所暗含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情况来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的实际水平不应该达到甚至接近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统治者或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能够令大多数人都处于最低生活标准。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这5个社会是被殖民强权或某个外国征服者统治,这些条件可能使得掠夺性榨取率达到异常高的水平。 [4]
对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和榨取率的计算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见解。它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古代社会往往会达到可能的最大不平等程度。只有在最富有的1%和由战士、管理者和商业中介组成的群体多于赤贫农业人口的社会,才可能会产生无限接近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榨取率。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我们可以从图A.2所描绘的大概估计具有的内部一致性中得到一些宽慰:似乎所有这些数据不太可能都使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犯错误,从而造成对以往不平等程度的严重误导。第二个重要的观察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最终降低了榨取率。这28个样本社会与2000年前后抽样的16个相同的或部分同延的国家之间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现象的规模(图A.3)。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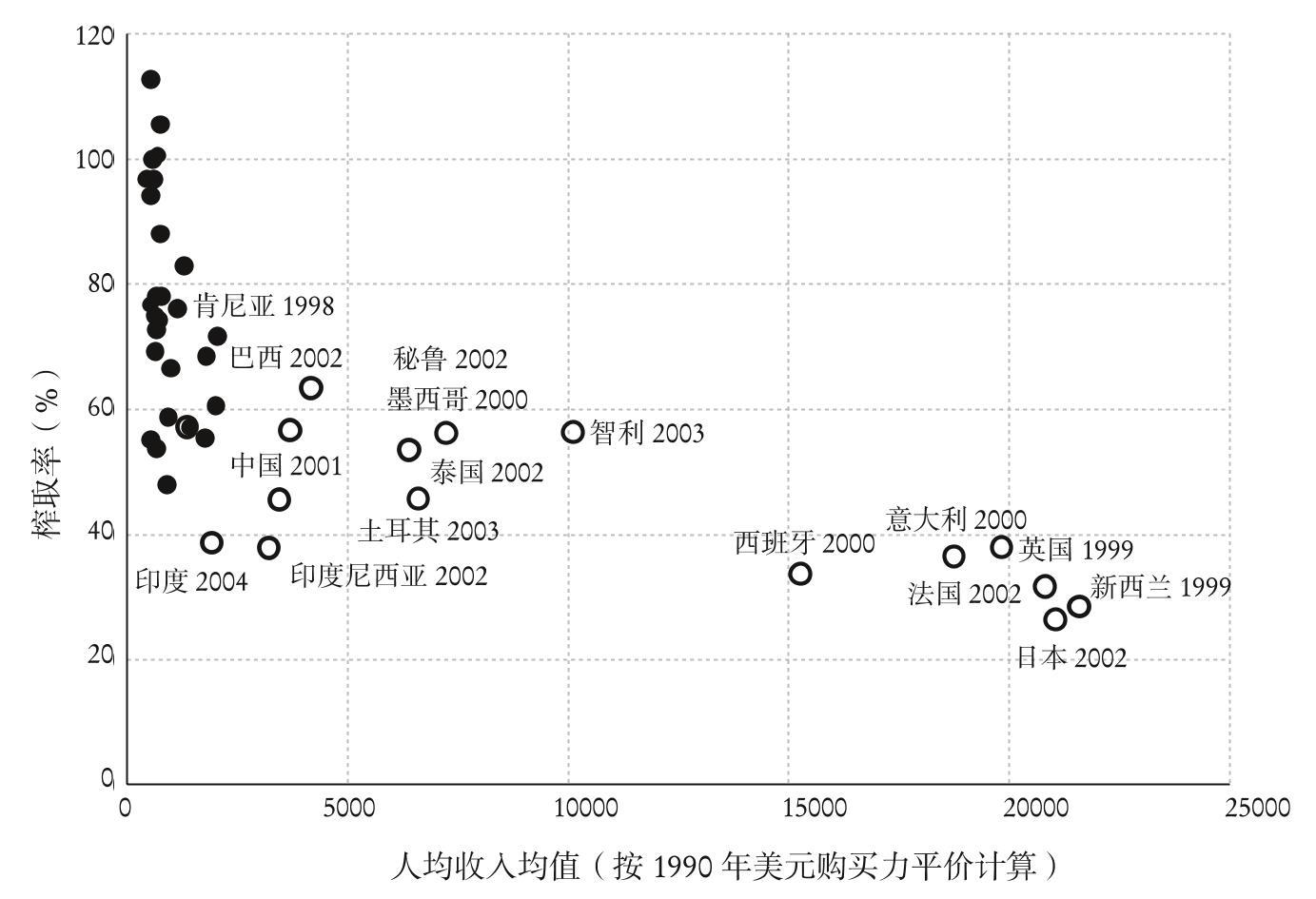
图A.3 前工业社会(实心圆)和相应的现代社会(空心圆)的榨取率
从榨取率观察到的不连续性表明,将收入基尼系数与差异显著的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多么令人误解。在0.45和0.41的榨取率上,前现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样本的平均基尼系数值非常相似。从表面数值看,它们仅能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平等程度只有轻微的弱化。然而,因为现代社会样本的平均人均GDP是前工业社会的11倍,所以平均榨取率就更低了——前者76%,后者只有44%。按照这种方法衡量,到2000年,这些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远远低于更遥远的过去。未经调整的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回想一下由1个富人和99个穷人构成的社会的例子,在这个虚拟社会中,平均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收入最高的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为5.7%。这一收入份额确实在2000年的丹麦出现过,当时丹麦的平均人均GDP不低于我假想例子中的73倍。差异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转化为表面上相似的不平等水平。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明显的:未经调整的估计历史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我所说的“有效不平等”的理解(理论上可行的和不平等程度相关的定义),结果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撇开这些数字的可靠性问题,英国在1290年左右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7、1688年为0.45、1759年为0.46、1801年为0.52,这表明不平等程度在逐渐增加,而这一时期大部分年份的榨取率都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下降——从0.69下降到0.57,在恢复到0.61之前下降到0.55。在荷兰,尽管榨取率持续下降,从76%到72%,再到69%,收入基尼系数却从1561年的0.56增加到1732年的0.61,然后下降到1808年的0.57。考虑到这些数字的巨大不确定性,给予其过多的重视是不明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榨取率比单独的基尼系数更能反映出真实的不平等程度。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更遥远的过去或当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不平等衡量方式将会高估现代社会中收入不平等的实际水平?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社会(虽然有很高的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矫正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有效不平等。对标准的不平等衡量方式的背景进行调整会带来很多麻烦。实际收入底线不是仅由维持生存的生理需要决定的,而且也由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决定。在介绍完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和榨取率的概念之后,米拉诺维奇通过考虑生存的社会维度改进了这一方法。低至300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的年收入确实足以维持生计,甚至还可能构成最低收入社会的可行标准。然而,社会规范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富裕而改变后,生存需要就相对上升了。今天只有在最贫穷的国家,政府贫困线才会与传统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致。而在其他地方,生活所需要的收入的最低限度提高了,因为它是更高的人均GDP的函数。对什么是构成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主观评价也表现出某种对整体生活水平的敏感性。亚当·斯密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最低需要的定义就是一个著名例子。按照他的观点,它们“不仅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代表这个国家使合乎道德之人免于不得体的生活,即使是处在最底层的人”,例如在英格兰,就是提供一件亚麻衬衫和皮鞋。尽管如此,贫困标准并没有以与GDP相同的速度发生改变,而是滞后于GDP的变化:它们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弹性是有限的。以该弹性为0.5来推算,米拉诺维奇证明,以社会最低生活标准调整后,给定人均GDP水平下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显著低于仅由生理生存最低需要所决定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一个人均GDP为1500美元的群体来说,它从0.8下降到0.55,而当人均GDP为3000美元时,它从0.9下降到0.68(图A.4)。 [6]
无论是否考虑变化的社会最低生活标准,1688—1867年间的英国和1774—1860年间的美国的榨取率都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将社会最低生活标准对GDP增长的0.5的弹性纳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性曲线的计算中,那么这两个时期的潜在榨取率大约为80%,远高于将观测到的不平等程度与最低生存标准联系在一起时计算出的那个约60%的数值。相比之下,自“二战”以来,无论以哪种方式定义的榨取率,都比实际低很多。在20世纪之前有效不平等一直保持在高位,因为当经济产出增长时,精英阶层仍然攫取了相对稳定的可获得剩余份额。这表明,除暴力压缩期外,有效不平等(受社会决定的最低生存底线的限制)在前现代时期和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很高。用基尼系数或最高收入者收入份额衡量的名义上的不平等,和由社会最低标准调整的实际不平等,都能维持大压缩之前收入差距非常巨大这一印象。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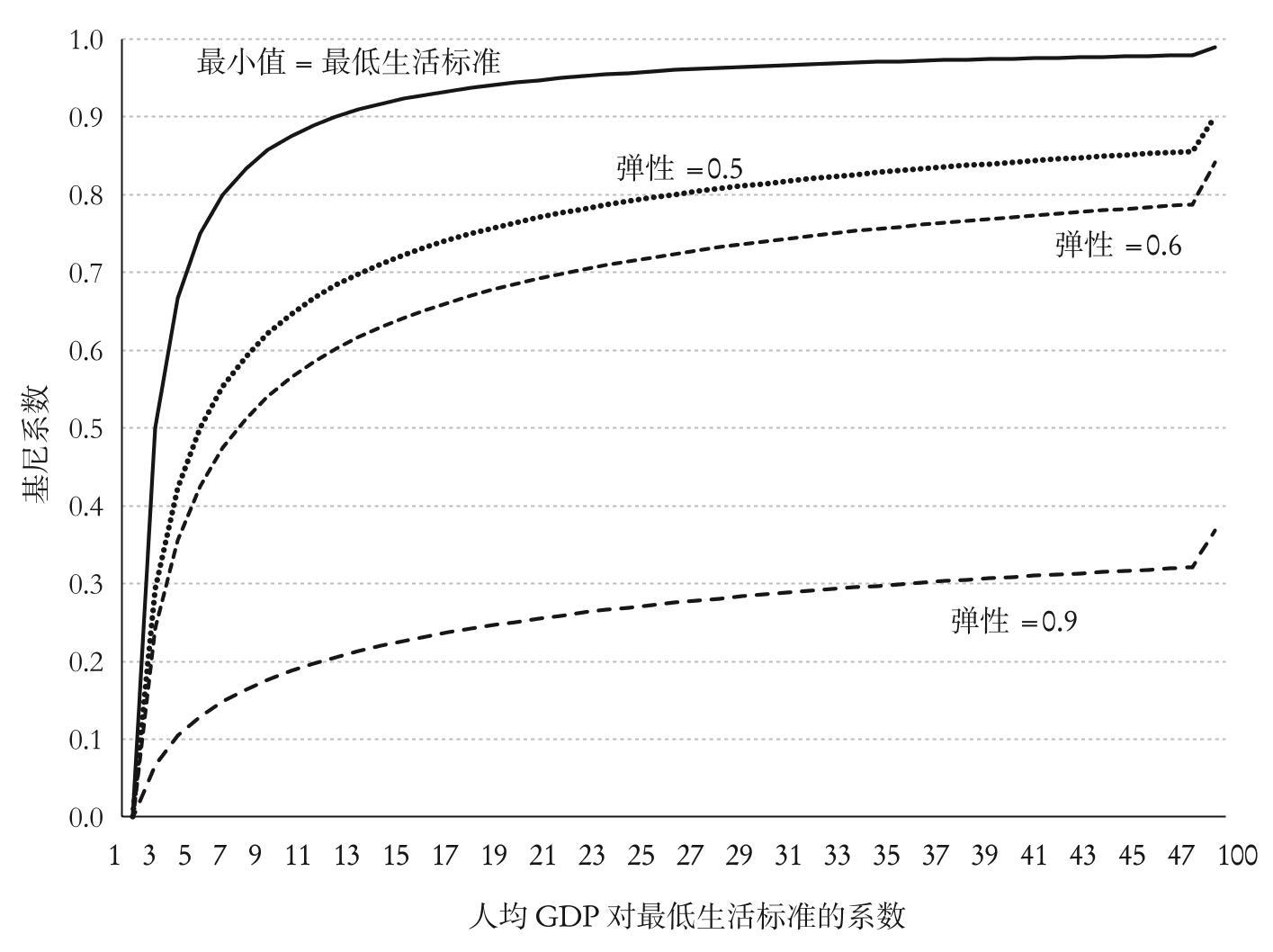
图A.4 不同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下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边界
但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无论是否按照社会最低标准进行调整,美国和英国的榨取率都在40%左右,即只有19世纪60年代的一半。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在最近的不平等水平反弹后,按照实际指标衡量,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比过去更符合平等主义呢?不一定。关键问题是这个:在一个主要不依赖化学燃料开采而依赖粮食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的经济体中,在给定的人均GDP水平下,经济上可行的最大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多少?在美国,当某一个人占有最低生存需要以外的所有剩余时,理论上可能的最大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99,而如果只占有社会决定的最低收入以外的所有剩余时,这一理论最大值约为0.9。为了使讨论更加便利,假定这种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尽管这可能需要这个垄断财阀雇用一支机器人军队来管控他的3.2亿同胞,我们必须问,它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年人均GDP为53000美元的经济体?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这样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将无法生产和再生产人力资本,也无法支持达到这些产出水平所需要的国内消费量(几乎占到美国GDP的70%)。因此,“真实”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一定低很多。 [8]
它会低多少?美国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现在接近于0.38。为方便讨论,假设它可能高达0.6,这是纳米比亚在2010年的水平,不至于将人均GDP降低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这将会产生一个63%的有效榨取率。在不同的设定下,米拉诺维奇曾认为,即使在相当极端的关于可行的劳动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假设下,美国总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6。但0.6的数值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是很高的:纳米比亚的人均实际GDP只有美国的1/7,而且它的经济高度依赖矿物出口。如果真实上限为0.5,那么美国目前的有效榨取率将为76%,相当于提到的那28个前现代社会的平均水平,也接近于美国在1860年的84%。在1929年,美国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不低于0.5,经社会最低标准调整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接近于0.8,这意味着榨取率约为60%。然而,即使是在1929年,当时的实际人均GDP不到今天的1/4,经济上可行的最大基尼系数应该低于0.8——比现在要高。在这一点上,尝试不同的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收获。如果能够衡量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那么也应该能够估算无法达到当前的产出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9]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潜力被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制约。在非常低的经济绩效下,不平等首先受到确保最低生活需要的产出量的约束。0.4的基尼系数(现代标准中的中等水平)在平均人均GDP仅是最低生活需要的两倍的社会里代表着极高的有效不平等,不平等的可能上限是0.5左右的收入基尼系数。在中等发展水平上,社会最低标准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例如,在1860年,当美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最低生活需要的7倍时,社会最低标准所隐含的最高可能的基尼系数或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为0.63,明显低于仅仅由基本生活需要所决定的0.86,有效榨取率也相应地从62%提高到84%。在那时候,由社会最低标准推导出来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几乎一定低于由经济复杂性所施加的上限:在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时代,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潜能将会相当高。当基于社会最低标准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或基尼系数上升到0.7和0.8的数量级时,即使在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下降时,这个结论也不再成立。这两个曲线边界将会在某个点上交叉,从而将后者转变成对潜在不平等的最强有力的约束(图A.5)。 [10]
我的模型表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在整个收入分配的历史谱系中都是相当稳定的。在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2~3倍的社会中,0.5和0.6数量级上的、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为最低生活标准5~10倍的、更为先进的农业和早期的工业化社会的、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非常相似,也和今天应用在相当于最低生活标准100倍的高收入经济体上的数值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改变的只是关键约束的性质,即从基本生存到社会最低标准再到经济复杂性。我把与直觉相反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经济绩效敏感性的缺乏称为“不平等的发展悖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另一个变体。这种长期稳定性对比较、评估超长期历史收入不平等有一个重大好处:如果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直接比较从古代到现在所有的基尼系数就是合理的。 [11]
当今美国或英国不平等的实际榨取率是否与150年前的一样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从那时到现在,它既没有变成原来的一半,也没有下降到仅根据社会最低标准计算所得到的水平。尽管当下美国的有效榨取率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于1929年的,但实际上,不平等现象仍然显著地在持续或反弹——以实际值计算。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如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无论我们怎样定义不平等可能性曲线,0.25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必然要比更为遥远的过去的低。我用一个关于对潜在不平等的约束如何影响国际对比的简要说明来结束这篇技术性的附录。在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上,美国究竟比瑞典高多少?给定基尼系数在0.23~0.38,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可以说比瑞典高出大约2/3。如果我们运用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来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最大值,这一比例不会改变:假定两国与GDP相关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都为0.6,美国的榨取率为63%,比瑞典的38%高出2/3。然而,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值不仅仅存在一个上限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为了维持高水平的人均产出,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需要显著大于0。插入一个最小可行的基尼系数,比如说0.1,加上之前的上限0.6,就会产生一个有50个百分点的不平等可能性空间(inequality possibility space,简称IPS)。观测到的瑞典不平等现象占据了这一空间的1/4,相比之下,美国则略多于一半。这种调整将使美国的用实际值衡量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至少是瑞典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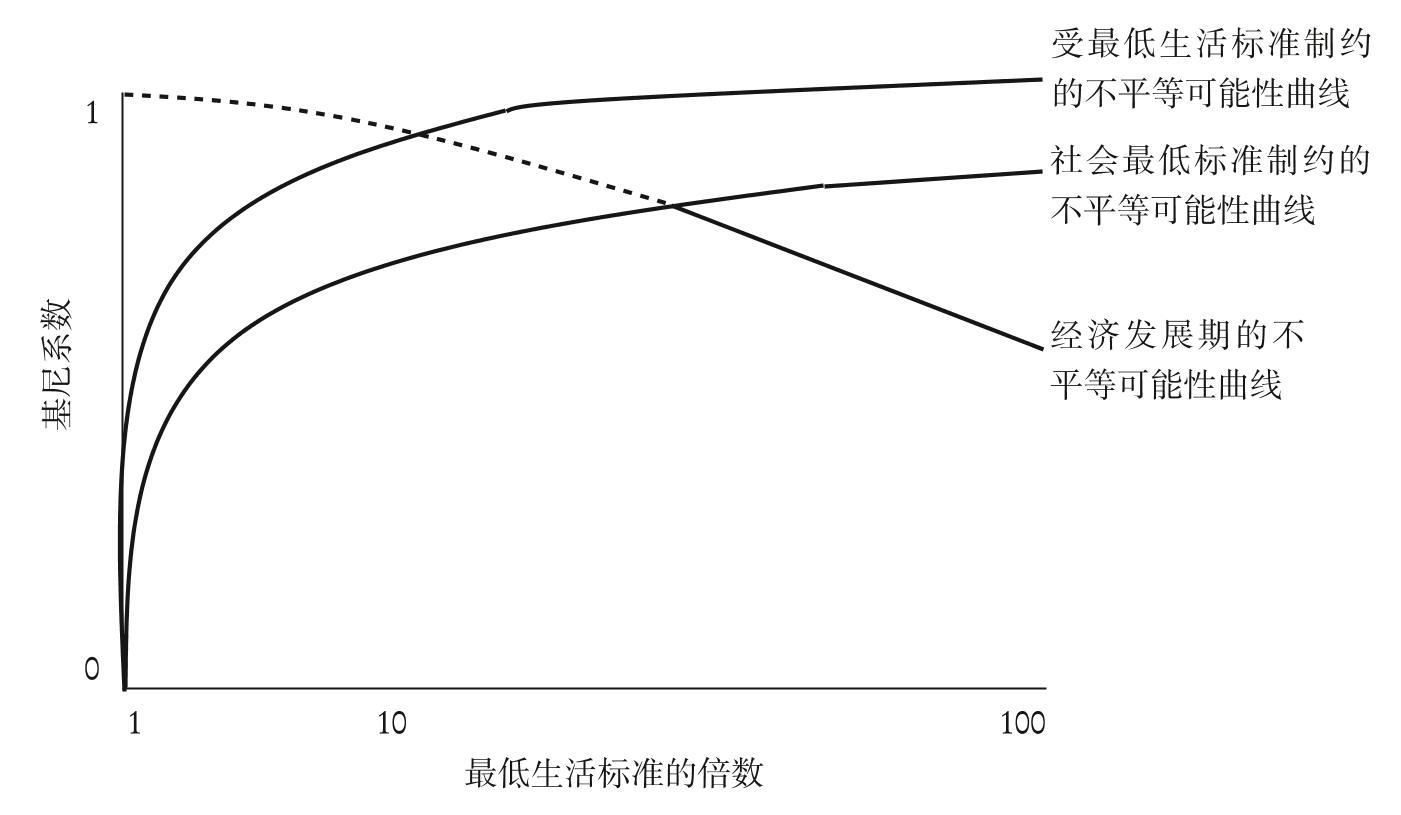
图A.5 不同类型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
[1]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56–259.Fig.A.1 based on their 258 fig.1.Modalsli 2015: 241–242 is more sanguine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existence below subsistence levels.For the notion of a maximum Gini of ~1 rather than 1, see herein,introduction, p.12 n.9.
[2] Maddison project.For a possible ancient forerunner, classical Athens, see herein, chapter 2,pp.84–85; but note that eve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tine Tuscany only reached about $1,000.
[3]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59–263 for the underlying data and their limitations.Fig.A.2 is based on 265 fig.2.Recourse to social tables produces a range of possible income distributions;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calculate two: one that minimizes and one that maximizes inequality within each income bracket.In most cases,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ch metrics are small.
[4]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263 table 2.Modalsli 2015:230-243认为,对社会表中的组内离散度进行恰当统计会导致相关社会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大幅提高:关于这些结果的大幅度离散,特别参见第237页图2。然而,考虑增加约15个百分点,会使基尼系数接近甚至超越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只有通过不断假设较低的生存底限或较高的人均GDP才能避免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指出,这些调整只能在极小程度上改变这些社会的相对不平等程度排名(238页)。关于用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作为非殖民化对收入不平等综合影响的代理变量的结果,参见Atkinson 2014b。
[5] Fig.A.3 from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11: 268 fig.4.
[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ii.k.Fig.A.4 from Milanovic 2013: 9 fig.3.
[7] Milanovic 2013: 12 table 1, 13 fig.4 (UK and United States).For high inequality up to 1914,see herein, chapter 3, pp.104–105, 108–110.
[8] 我排除了石油国家,因为它们能够使高收入不平等水平与高人均GDP共存,事实上它们也确实存在高收入不平等水平与高人均GDP共存的经济。依赖于其他矿物开采形式的经济体,如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也是非常不平等的,但它们未能达到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关于美国和英国的数据,参见Milanovic 2013:12 table 1。我没有使用其美国市场收入不平等数据,因为它们与这里的讨论不相关。
[9] Data: SWIID; Maddison project; Milanovic 2013: 12 table 1, with Atkinson 2015: 18 fig.1.1.See Milanovic 2015 for an upper limit of 0.55 to 0.6.Only market income Gini figures appear to be avail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9, but considering the low levels of taxation and transfers at the time,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much higher than those for disposable income.For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growth, see herein, introduction, p.19.
[10] For the data, see, once again, Milanovic 2013: 12 table 1.我的简单模型忽略了其他必定会产生影响的因素——最显著的政治制度。
[11] 参见Scheidel and Friesen 2009,网络媒体报道称,当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罗马帝国时期,这是基于没有考虑现代的市场再分配和各自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市场基尼系数的一项观察:http://persquaremile.com/2011/12/16/income-inequality-inthe-roman-empire/,部分报道参见: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12/19/usincome-inequality-ancient-rome levels_n_1158926.html。只有在当今美国的实际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值降低至0.5时,这一论述才正确。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经济不平等可能直到最近才重新在流行的话语中变得非常突出,但实际上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我的这本书旨在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
最早使得我对这种久远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之一就是布兰克·米拉诺维奇,他是不平等研究领域世界级的专家,其研究一路回溯到远古时期。如果有更多像他一样的经济学家,会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听相关观点。大约10年前,史蒂夫·弗里森让我更加努力思考古代的收入分配,与伊曼纽尔·赛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度的一年则进一步激起了我对于不平等研究的兴趣。
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保罗·西布赖特邀请我于2013年12月在图卢兹高等研究院讲授一次杰出讲座,这促使我将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杂乱思想转变成更为一致的论点,同时也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项目。在圣菲研究所进行的第二轮早期讨论当中,山姆·鲍尔斯证明了他是一个激烈而友好的批评家,苏雷什·奈杜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当我的同事肯·舍韦要我代表斯坦福欧洲中心组织一次会议的时候,我抓住这次机会,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探讨历史长河中的物质不平等演变。我们2015年9月在维也纳的会议是愉快且富有教益的:我要感谢这次会议的当地协办人员,伯恩哈德·帕尔梅和皮尔·弗里斯,还要感谢肯·舍韦和奥古斯特·赖尼西的资金支持。
我从在埃佛格林州立学院、哥本哈根大学、伦德大学,以及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论文报告所获得的反馈意见中获益良多。我很感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乌尔丽克·克罗特斯琴、皮特·邦、卡尔·汉普斯·吕特肯斯、刘津瑜和胡玉娟。
戴维·克里斯蒂安、乔伊·康诺利、皮特·加恩西、罗伯特·戈登、菲利普·霍夫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乔尔·莫基尔、热维尔·内茨、谢夫凯特·帕慕克、戴维·斯塔萨维奇和彼特·图尔钦对整个书稿进行了阅读和评论。凯尔·哈珀、威廉·哈里斯、杰弗里·克朗、皮特·林德特、约什·奥伯和托马斯·皮凯蒂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开会讨论了我的书稿,同时我要特别感谢贡纳尔·林德和简·佩德森所提供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在一些特定章节和问题上,得到了来自安妮·奥斯丁、卡拉·库尼、史蒂夫·哈伯、玛丽莲·马森、迈克·史密斯和加文·赖特宝贵的专家意见。我没有像本来应该的那样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要特别感谢一些同事,他们慷慨地和我分享自己还未发表的作品:吉多·阿尔法尼、凯尔·哈珀、麦克·朱尔萨、杰弗里·克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伊恩·莫里斯、亨里克·莫瑞滕森、约什·奥伯、皮特·林德特、伯恩哈德·帕尔梅、谢夫凯特·帕慕克、马克·皮泽科、肯·舍韦、戴维·斯塔萨维奇、皮特·图尔希和杰弗里·威廉森。布兰登·杜邦和约书亚·罗森布洛姆两人编制并分享给我的美国内战时期的财富分配数据对本书非常有帮助。莱昂纳多·加斯帕里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谢夫凯特·帕慕克、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肯尼斯·舍韦、米哈尔·斯坦库拉、罗伯特·斯特凡和克劳斯·瓦尔德非常友善地寄给我数据文件。斯坦福大学主修经济学的安德鲁·格兰纳托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助理工作。
我在2015—2016学年被斯坦福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资助期间完成了这一项目:我要感谢我的院长——德伯拉·萨兹和理查德·萨勒,他们支持了这件事(在很多其他人提供的支持以外)。这次学术进修使我得以在2016年的春季作为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那里完成整个书稿的整理。我要感谢这些丹麦同事的热情款待——尤其感谢我的好朋友和系列论文的合作伙伴皮特·邦。我想用也许有些笨拙的感谢之词对古根海姆基金会授予我奖金来完成这一项目表达谢意。虽然我有幸在正式拿到这笔奖金之前就完成了这本书,但我确定自己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会充分地利用好它。
在这一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乔尔·莫基尔善意地将这本书放到了他编辑的系列丛书当中,并且帮助它通过了评审过程。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和明智的评论。罗伯特·滕皮奥是一位非常棒的激励者和编辑,也是一位真正的书籍爱好者和作者的拥护者。他提供了关于本书主标题的建议,我也因此欠了他的人情。他的同事埃里克·卡拉汉使我能够及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两本相关书籍的清样。我还要感谢珍妮·沃尔克维基、卡罗尔·麦吉利夫雷和乔纳森·哈里森,他们确保了整个出版过程非常顺利和迅速。当然,还要感谢克里斯·费兰特为本书的英文版设计了非常精美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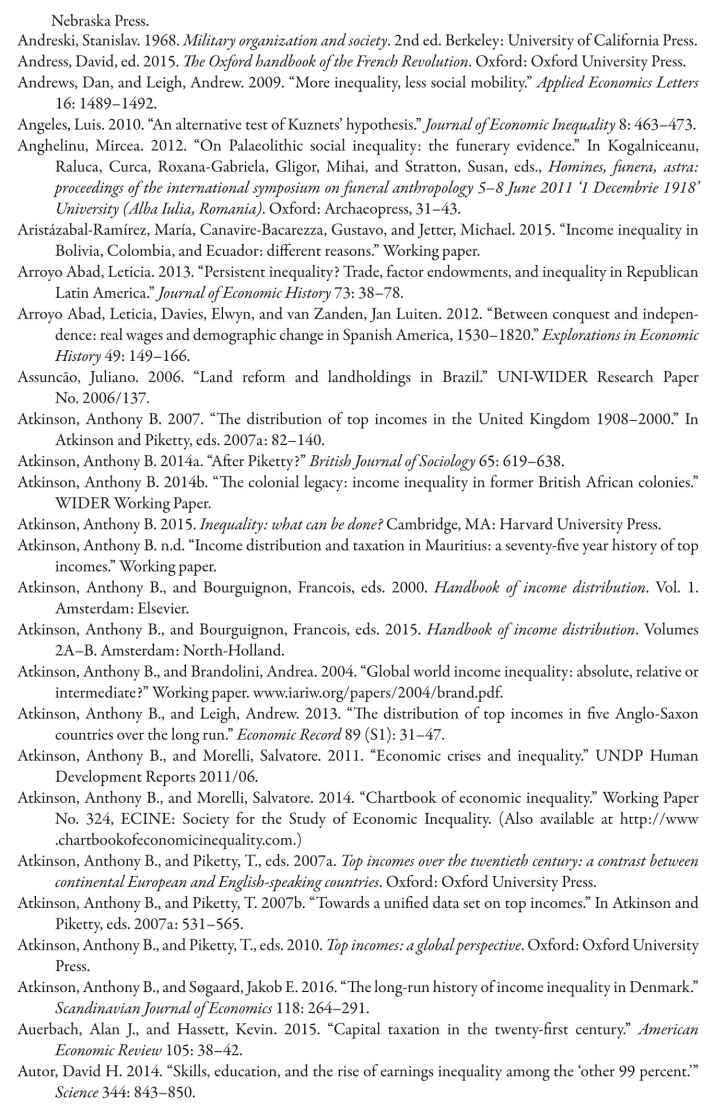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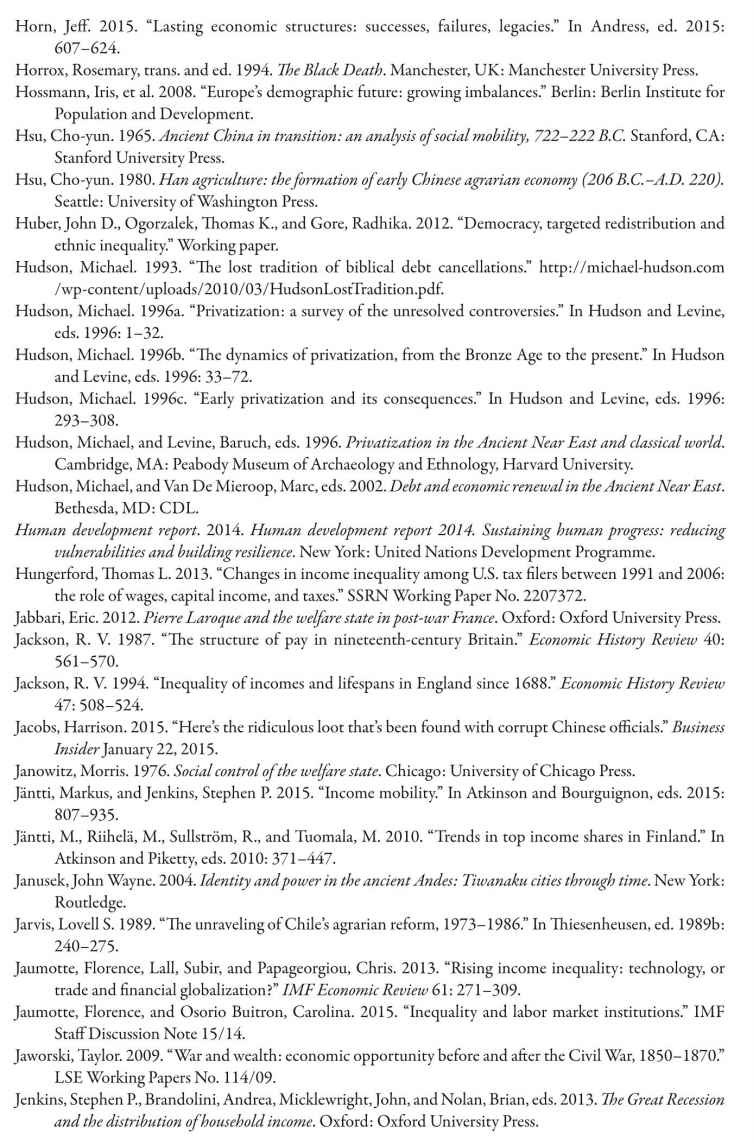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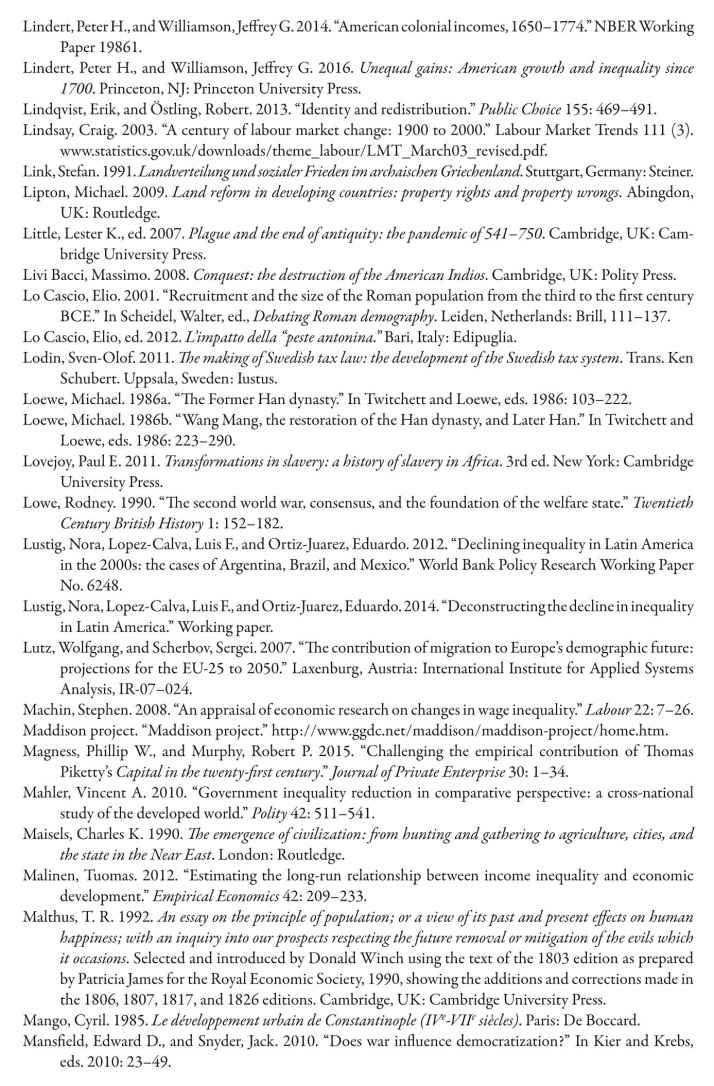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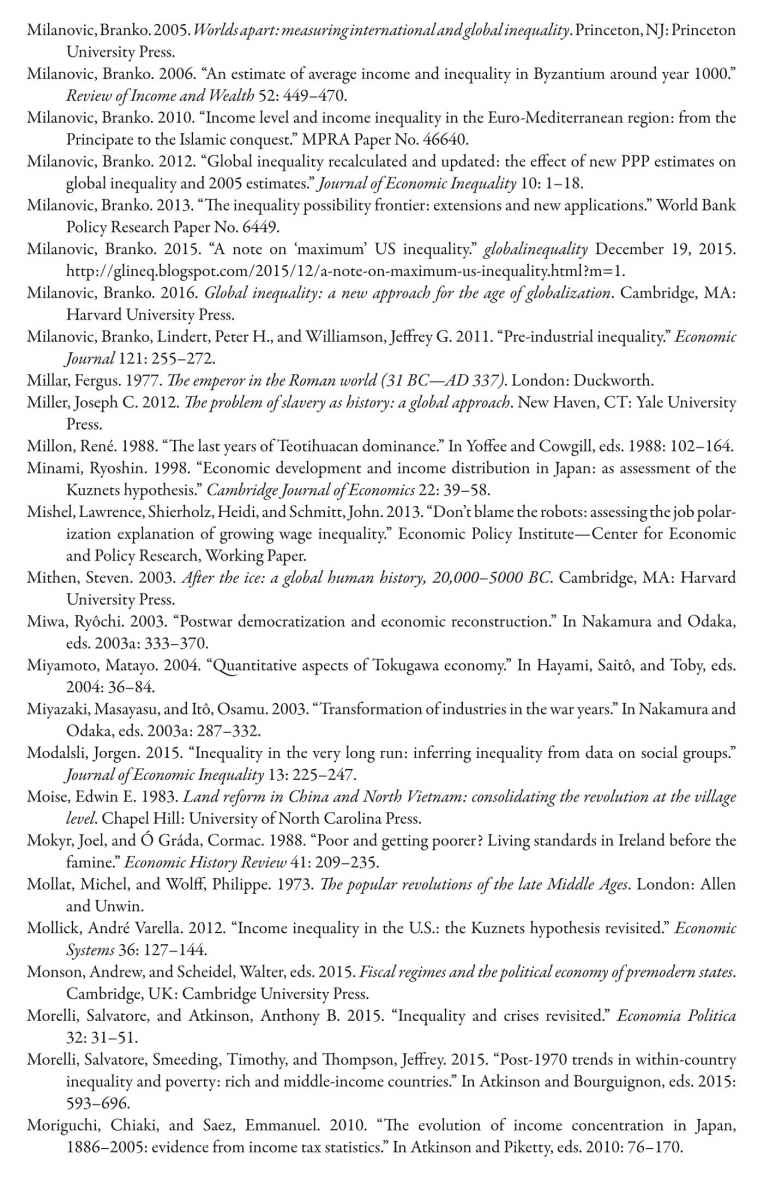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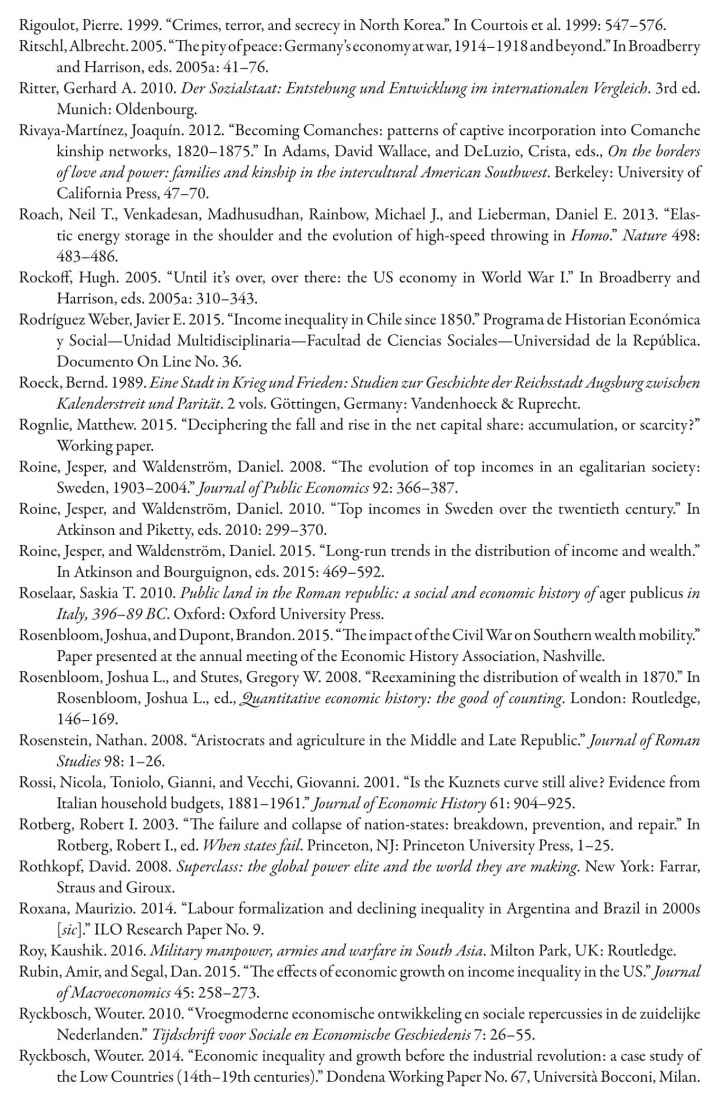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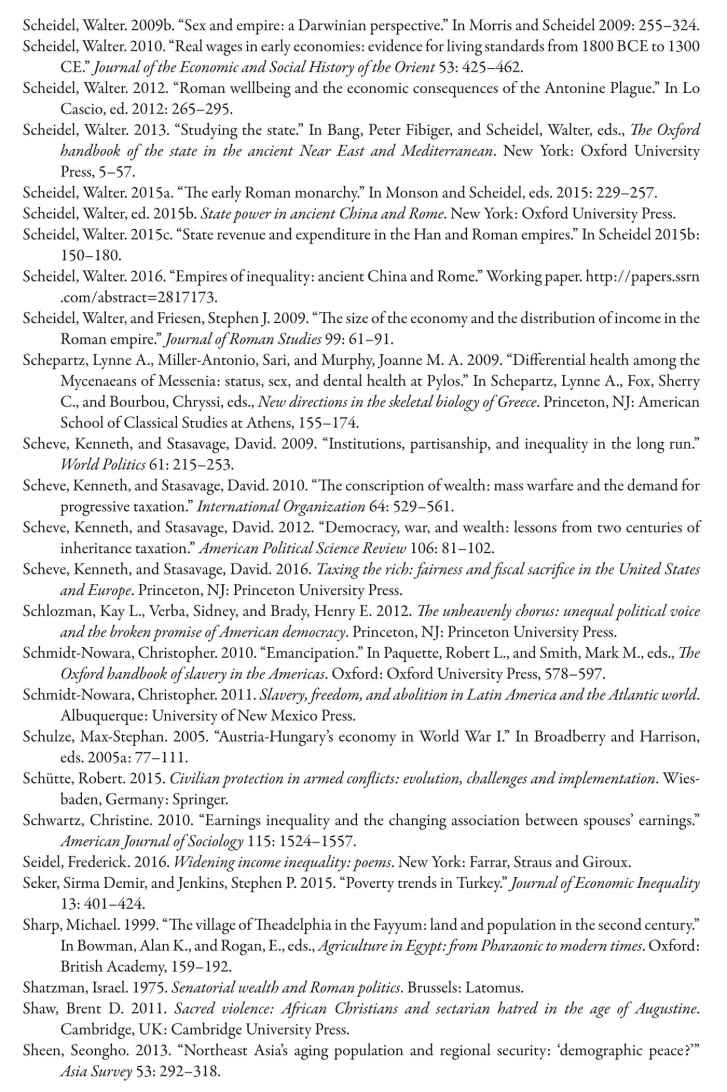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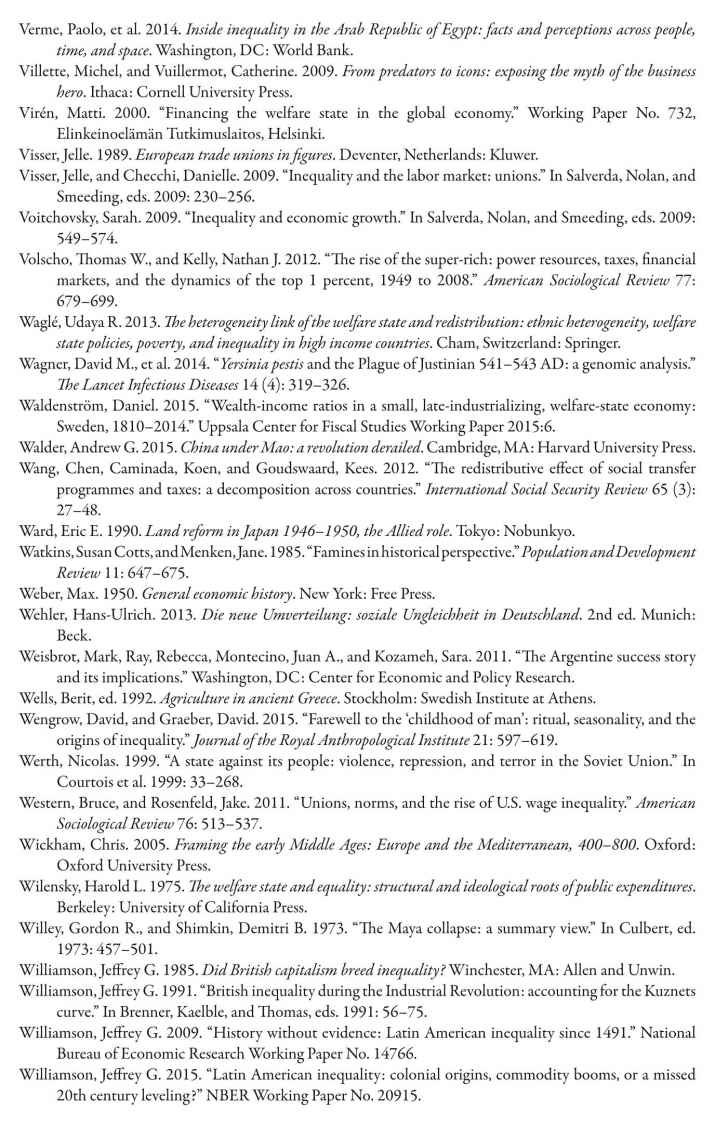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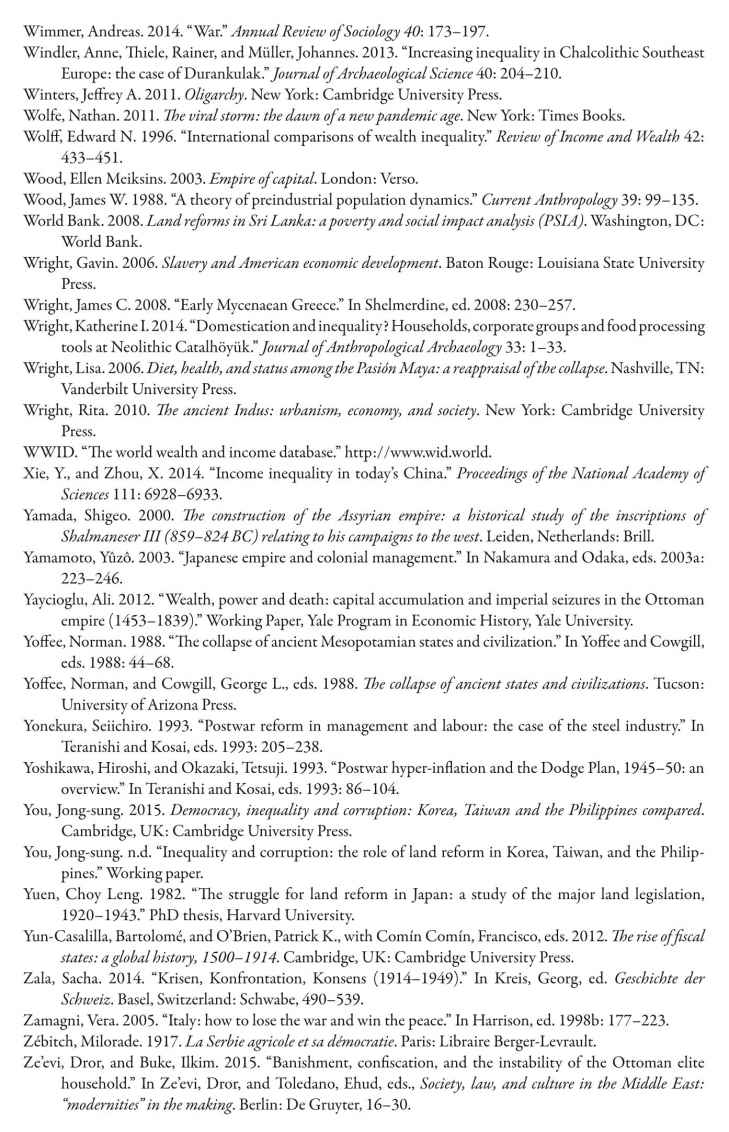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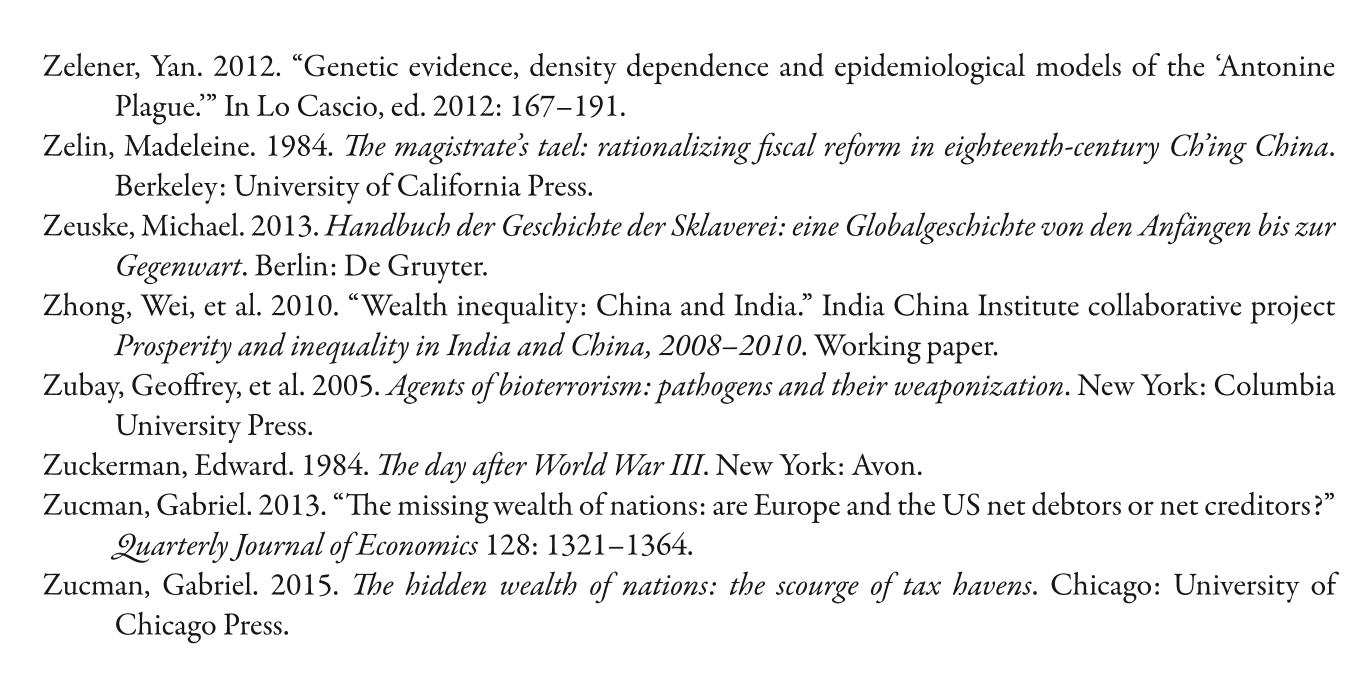
《不平等社会》一书的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2017年推出的这部新著论及暴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的矫正机制即“天启四骑士”——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其矫正功能在于屡次摧毁了富人的财富,大大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暴力和不平等问题是自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新见解,沃尔特·沙伊德尔观点如下。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差距(尤其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并且一直是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沙伊德尔通过追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史,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暴力性冲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中起关键作用。他进而揭示了暴力和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当大屠杀和灾难降临之时,不平等程度会下降,而当和平与稳定回归的时候,不平等程度会上升。《不平等社会》从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他认为,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其二,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比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瘟疫(“天启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结果。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每一次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驱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之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其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还有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种族和民族方面的不平等,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乃至机遇的不平等。尤其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完全准确。
其四,即使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也主要聚焦于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主要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着眼于暴力冲击及其替代机制,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
其五,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占比。尤其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两者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即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对分配的模型提供急需的深入理解。
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0世纪前很少有国家定期征收收入所得税。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资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用来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然而,即使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例如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最有希望成为不平等的标志——实际上往往是唯一的参照系数和坐标。
其六,《不平等社会》详细探讨了1980—2010年部分国家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1980—2013年20个OECD成员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还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调查,因此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土重来。
2018年2月7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最新论文。文中最新数据显示,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0%的财富,财富不均的情况类似于100年前的情况,百年历程走出一个大大的“U”形。1929年,美国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顶层0.1%群体占有该国25%的财富,且顶层10%的群体居然坐拥高达84%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均的情况虽然在经济大萧条、“新政联盟”和“二战”带来的经济下滑后有所缓解,但从80年代开始,情况再度恶化,以至今天已和百年之前相差无几。据《北美留学生日报》引用的“消费者财务调查”的数据,美国顶层1%群体仅包括126万户家庭,却占有近40%的财富,平均每户拥有2680万美元财富,是普通家庭拥有的69万美元的40倍甚至更多。福布斯评出的全美前400位富豪(其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00025%)的资产总和超出了底层1亿5000万美国人的资产总和。
沙伊德尔强调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颇为严重的不平等,尽管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或者市场和权力,乃至全球化或者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例如,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翻了一番,相应的财富集中度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
其七,《不平等社会》最后提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目前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并不少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出了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长长的清单。与皮凯蒂的关注点在税收上一样,与安东尼·阿特金森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一样,作者也对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税收改革方案情有独钟。
《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关于暴力和不平等史的某些新见解,许多统计数据、不平等的测量工具和方法等,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如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稳定社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不平等社会》无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材料。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姊妹篇。该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连续数周在亚马逊网站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被称为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是,反驳者和批判者并不少见。《华尔街日报》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丹尼尔·沙克曼)。《经济学人》撰文对书中预测的未来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克里夫·克鲁克)。
皮凯蒂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用详尽的(尽管富有争议的)数据全面分析了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收入与财富的分布变化,从而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讨论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强大力量。除“二战”时期之外,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即r >g ,因此财富趋向于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除了r 和g 这两个变量之外,作者进而探讨了帕累托分布与分配中所获份额的关系,此外,一些核心的宏观经济因素也对帕累托分布的参数产生了影响。
他对于库兹涅茨曲线以及良性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旨在证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现象近几十年来已经日益扩大及日趋严重,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这本书争议不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无独有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本书致谢中承认:“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他在序言“不平等的挑战”中,开门见山地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判断作为醒目的标题。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例如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共同的主题是探讨不平等问题,而且在于都致力于对于历史数据的收集工作。前者涉及的时空更为宽广,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还包括各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例如,图11.2的标题是“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图11.3列举了“公元100年—2世纪60年代和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实际价格与租金变化。图11.4统计“奥格斯堡的财富不平等:纳税人的数量、平均纳税额以及纳税的基尼系数,1498—1702年”。
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是不平等问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和人文主义传统,而且从这一视角,阐释“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因此衍生出以人为本思想、大同社会理想、民本主义思想,国家以养民为本且行养民之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
在中国哲学史上,法家代表人物荀子首先提出了“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的命题,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进而提出要以礼来调节经济生活,必须“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治国理家和财富分配则倡导公正、公平和均平,“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礼记·礼运》更是提出了大同社会应财产公有的主张。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一是推崇“圣人不积”,对私有财富过多积累持否定的态度,原因在于富或求富是祸乱之源;二是倡导“天之道”和“人之道”合一。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老子》)。这是阐述“损”与“补”、“有余”与“不足”的转化辩证法,以及“天之道”应该与“人之道”具有同一性,主张“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损有余以奉天下”,从而改变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天道”就是均安、均平、均富,即“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体现了崇尚社会财富均等化的道家学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以及历代农民运动领袖提出以“等贵贱,均贫富”为标志的关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就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管仲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政策以矫正贫富不均,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秦国商鞅变法的精髓是“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引发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矛盾有所缓解。
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尤其财富观念以及财富分配主张,与神话紧密相连。
荷马和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归结为神的惩罚,后者进而将其归咎于人德行的堕落,提出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合乎正义者理应得到荣华富贵。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一个自由人的人生目的是培养神所赋予的善德和追求正义,追求财富要合乎道德的公正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财富。这是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强调从正义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之理论渊源。柏拉图认为贫富悬殊会使城邦分裂为贫与富两大对立集团,贫富差距过大还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一观点与孔子的基本一致。亚里士多德肯定人们追求财富,但要用“中道”的原则来把握追求财富的度,这个度就是灵魂的善,并且要使灵魂的善高于财富的善。这里所强调的正义和灵魂的善最终来自神。他还从商品交换的角度阐释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
古希腊罗马的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接踵而来的中世纪的经济思想,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伦理和神学文化。教会思想家阿奎那,更是处处着眼于基督教教义。
现当代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一般而言,绝对平等或者纯粹平等的社会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所以《不平等社会》主要是阐述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特征的经济不平等,基本上舍弃了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其他不平等类型。
应该强调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不仅不会拆除不平等的藩篱,就其大趋势而言,是在扩大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四大矫正力量或者“四大骑士”,即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尤其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或者改朝换代时期时,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大为改观。
例如,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使用暴力剥夺劳动者,消灭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过程,它不是田园诗式的过程,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1867年)。但另一方面,这是“工业骑士”战胜“佩剑骑士”的历史过程,在反对封建特权、争取平等,反对专制束缚、争取自由方面有它的历史进步性。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因此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恩格斯,1894年)。
又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彻底消灭不平等现象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也就是这个平等的权利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875年)
怎样消灭这种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们寄希望于“减税”,前提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乌托邦政策。《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制度,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将自行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时候,不平等现象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暴力也是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是歌颂“革命”性暴力较早的文献记载,并且,在中国,暴力观念往往与“人性善”和“人性恶”孰是孰非的争论相联系。中国数千年的统一与分裂不断循环的历史,也与恶、暴力或战争息息相关。
西方学者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阐述善恶辩证法的黑格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以及《论暴力》的作者乔治·索雷尔和《论革命》的作者汉娜·阿伦特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专辟三章“暴力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和不平等理论,对于读者正确阅读《不平等社会》大有裨益。
这本书以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博大视野和宏大叙事风格,回顾了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战争和暴力史。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暴力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着革命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什么是遵循唯心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鼓吹“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杜林),并且采用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暴力”。在杜林看来,人类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原罪,而且任何暴力“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
什么是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言以蔽之,“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反杜林论》)。
因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私有财产的形成,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其出现和形成都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暴力在这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暴力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暴力具有二重性。形而上学的杜林先生把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他的暴力史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历史是谁创造和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答案不是杜林的暴力创造历史观,也不是黑格尔所标榜的“恶”“英雄”“杰出人物的动机”创造历史,或者“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在晚年提出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在他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们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与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不平等社会》一书,由颜鹏飞主持翻译和初校。各章译者如下:序言等,颜鹏飞;1~3章,12章、13章,李酣;4~6章,曾召国7~9章,甘鸿鸣;10章、11章、15章、16章、附录,王今朝;14章,刘和旺。原文个别地方做了删除处理。
颜鹏飞 2019年2月5日 于珞珈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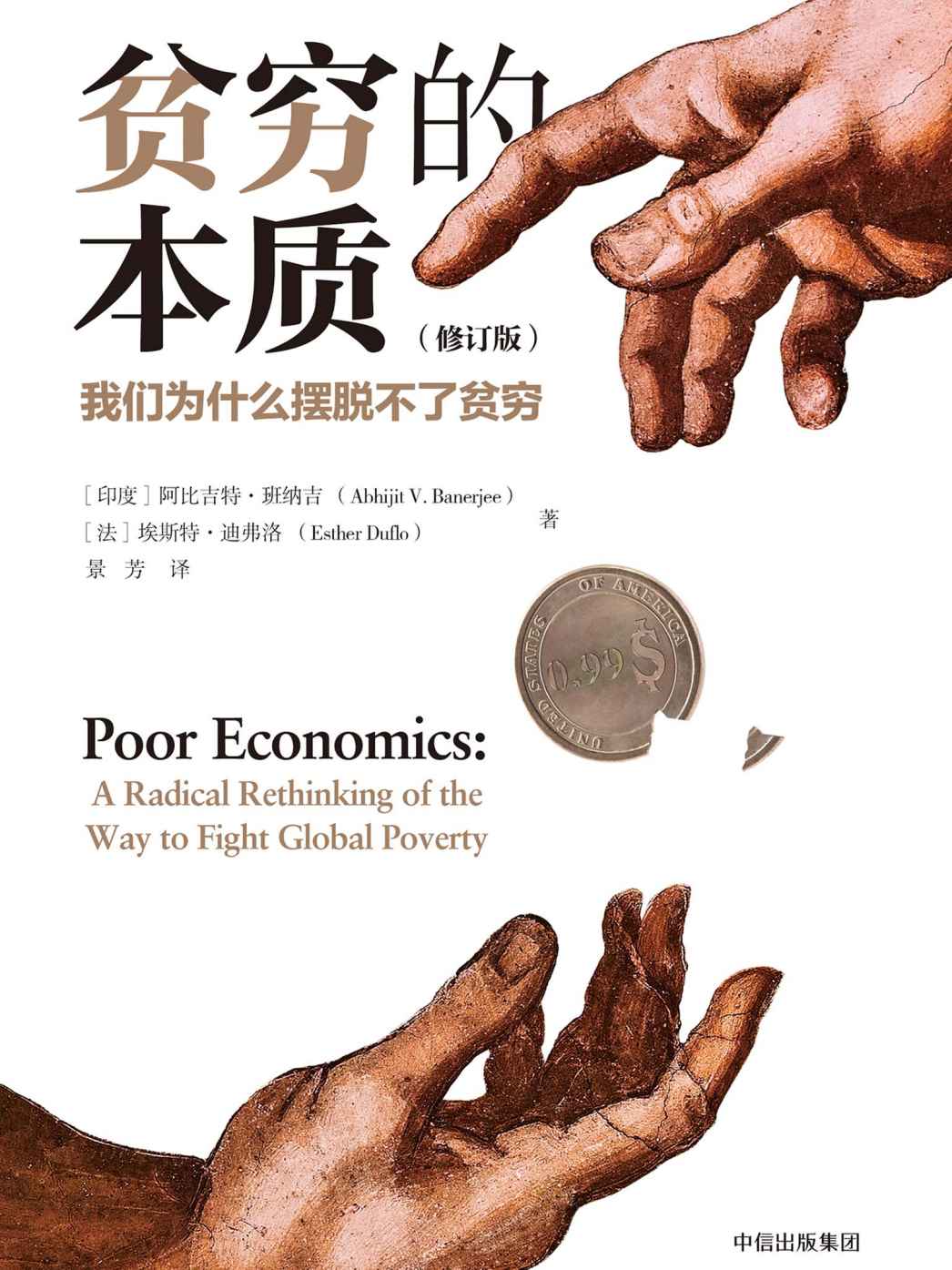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母亲:
妮玛拉·班纳吉和维奥莱纳·迪弗洛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他们知道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他们对自己及别人的期望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做出选择?显然,两位作者通过个人行动和公共行动赢得了多次富有意义的小胜利,为全球穷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还可能会像滚雪球似的继续下去。这本书令我非常着迷,让我对穷人摆脱贫困充满了信心。
——罗伯特·默顿·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见解极为深刻的好书,由两位专门研究贫穷本质的优秀作者写成。
——阿马蒂亚·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心理学教授
对于每一位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我很久没读过能让我学到这么多的书了。《贫穷的本质》堪称经济学的最大献礼。
——史蒂芬·列维特
《魔鬼经济学》作者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这本书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超越了关于贫穷问题的简单分析。书中充分论述了贫穷家庭为改变现状而面临的挑战,展现了他们为摆脱当前贫穷而迁居的努力,并用真实的数据对其加以验证。《贫穷的本质》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本书在探讨贫穷核心问题的同时,保留了对乐观主义精神及更多答案的寻求。
——南丹·纳拉坎尼
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印度身份证管理局主席
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这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例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
——《卫报》
这本书中,作者进行了大胆的研究,亲身体验并描述了全世界至少8.65亿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0.99美元)的真实生活。
——《经济学人》
这是一本极有说服力的读物,它真实再现了穷人的生活,很有可能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福布斯》
这是一本非凡之作,读后收获颇丰。《贫穷的本质》是对穷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中边缘生活的细致描述。两位作者清晰而又富有同情心地描述了他们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为事实、假设和思辨开创了全新的视角。正因如此,这本书值得一读。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除了记录大量的亲身体验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对穷人生活的个性化描述。它反映了贫困人群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此类书籍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代表了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的实践方向。
——《金融时报》
这本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俨然是一部为贫困人口量身定制的《魔鬼经济学》。书中有很多从我们所服务对象角度出发的有关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入见解。他们唤醒了我们共有的人性,并提醒我们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见略同。
——《快公司》
随机对照实验是解决贫困问题常用的方法。这本由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什么形式的援助最有效?”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科学、深刻、观点清晰、通俗易懂的书,是对国际援助持支持或反对意见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和对贫困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必读之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罗伯特·默顿·索洛以及经济学畅销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倾心推荐之作。我觉得你最好读一读这本书,它将开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讨论话题。
——美国《金融世界》
这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须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
——《印度快报》
两位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连续15年对全球贫困问题做出了精妙的研究,并探求我们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原因。这本书论点清晰、有理有据,颠覆了以往研究贫困问题的传统方法,不失为关注此类问题的读者的醒脑之作。
——《柯克斯评论》
埃斯特6岁时曾读过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0.93平方米。当时,埃斯特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棋盘,由许多个3英尺×3英尺 [1] 的小格子组成,每个小格子只能挤进去一个“小兵”。她当时就思考着,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24岁时,埃斯特终于来到了加尔各答市,当时她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埃斯特向窗外望去,眼前的一切令她有些失望。每个角落都空无人烟,只有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空草坪和孤单的人行道。那本书中刻画得触目惊心的困境在哪里,那些拥挤的人群都跑到哪里去了?
阿比吉特6岁时就知道加尔各答市的穷人住在哪儿,他们就住在他家后面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那些穷人的孩子似乎总有玩的时间,他们擅长玩各种游戏。如果阿比吉特和他们玩弹球,最后弹球总会跑到他们的破裤兜里。对此,阿比吉特心里很是不服气。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毫无疑问,有些政策取向与这种针对穷人的看法相一致,如“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呼吁人权至上”“先解决冲突”“给最贫穷的人多些资助”“外国援助阻碍发展”等。然而,这些想法却无法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
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遗憾的是,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我们是学者,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们构建理论,研究数据。然而,我们研究的性质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时间与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分子、政府官员、医疗保健工作者及小额信贷者接触,进行基础性研究。我们来到街头巷尾,村前屋后,与住在那里的穷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搜寻数据信息。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路过而已,却始终被他们当作客人来对待。即使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无多大意义,他们也会耐心解答,并同我们分享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回到办公室后,我们一边回顾那些故事,一边研究数据,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甚至迷惑不解。我们难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那种(西方或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发展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穷人生活的看法联系起来。有时,强有力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评估甚至放弃我们所坚持的理论。然而,我们会尽量先搞清楚,我们的理论为什么行不通,怎样利用该理论更好地描述世界。本书就产生于这一思想交叉点上,展现了我们所编织的一个关于穷人生活的完整故事。
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就全球穷人最多的50个国家来说,其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各国政府将生活费低于这一水平的人定位为贫穷状态。根据写作本书时的汇率标准,16卢比相当于36美分,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较低,如果穷人以美国的物价水平来购物,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99美分。因此,要想知道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你就要想象如何在迈阿密或莫德斯托每天只靠99美分生活。要用这点钱购买你一天所需(除了住房),这并不容易。比如,在印度,99美分只能买15根小香蕉,或是3磅劣质大米。你能靠这点吃的活下去吗?不过,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都是这样生活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然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会在这些方面细细思量。
每天99美分的生活意味着,你接收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报纸、电视和书籍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你常常会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比如说,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你的孩子患上麻疹。这就意味着,在你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多机构并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而建的。大多数穷人都没有收入来源,更不用说基于自动缴纳的退休计划了。这就相当于,在你大字不识的情况下,你却要根据很多细则做出决定。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他怎能读懂一份包含大量拗口病名的健康保险产品呢?
一切都表明,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花费、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
要想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再加上一点儿援助(一条信息、一点儿推动),有时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另一方面,错位的期望、必要信仰的缺乏、表面上的一些小障碍,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持住正确的杠杆至关重要,但正确的杠杆往往很难找到。而且,单凭一个杠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贫穷的本质》一书揭示了穷人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穷人能实现什么,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一些助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些助力。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阐述了一种如何找出这些难点并攻克这些难点的方法。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晰窥见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他们都会买些什么;他们会为子女的教育做些什么;他们会为自己的健康、子女的健康以及父母的健康做些什么;他们会生几个孩子等。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阐述各类市场及机构能为穷人做些什么:他们能借钱吗?能存钱吗?能为自己投一份人身伤害保险吗?政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在何种情况下政府会力不从心?自始至终,本书都在讨论几个相同的基本问题。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遇到了哪些障碍?是起步的花费较大,还是起步容易维持难?为什么花费会这么大?穷人意识到福利的重要性了吗?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呢?
《贫穷的本质》一书最终揭示了穷人的生活及他们相应的选择,对于我们消除全球贫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的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医疗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本书还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不只是有象征性的作用,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指出了希望与知识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1] 1英尺约为0.3048米,3英尺约为0.91米。——编者注
不 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拯救儿童” (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第一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 )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最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援助问题而争论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一个前提,即我们应在力所能及时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哲学家彼得·辛格曾写过关于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准则,他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件价值1 000美元的衣服,换取一个落水儿童的性命。辛格还认为,这名落水儿童就是那些每年活不到5岁的900万儿童之一。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的确,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荒废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这个非洲小女孩来说却影响很大:她可能沦落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妓女,将病毒传染给一个来到非洲旅游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人又会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她可能会患上一种耐抗生素的肺结核,这种病毒最终可能会传播到欧洲。如果她当初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她可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药,或者就像中国小姑娘戴满菊一样,她上学的机会来源于银行职员的一个疏忽,这可能使她最终成为雇用上千人的商业巨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在其著作《半边天》(Half the Sky )中讲述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即使她没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又有何理由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分歧便会显现。辛格关于帮助别人的观点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知道如何去做。在你不会游泳的前提下,甘愿牺牲一件衣服的道德准则便显得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在《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 )一书中,辛格不辞辛苦地为读者列举了很多实例,告诉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伸出援手。在辛格的网站上,这部分内容是定期更新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也是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中呢?
只要拿出约10美元,一个家庭就能得到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还会有人教他们怎样使用这种蚊帐。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向家长们免费提供这种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答案却不甚明了。很多“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如果玛丽睡在蚊帐中,约翰就不太可能被传染——如果至少有一半人口睡在蚊帐中,另一半人口即使没睡在蚊帐中,他们被传染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问题是,睡在蚊帐中的孩子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1/4。对于马里及肯尼亚的很多家庭来说,10美元的花费有些高。考虑到使用者及社区中其他人的利益,以优惠价销售蚊帐或免费赠送蚊帐似乎是个好办法。的确,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伊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解释这一争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以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免费赠送的,或是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并比较几组人在面对不同程度优惠价时的行为。这里,我们着重于“比较”,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
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可能都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而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会被某家非政府组织选中。不过,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从他们使用蚊帐的方式上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这些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方式就是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的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开展了这样一项实验,随后,其他研究人员分别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迪帕的实验中,随机选定的几个人在购买蚊帐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通过对几个小组在接受不同价格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迪帕便能回答我们前面列出的三个问题,至少在这项实验的背景下是这样的。
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将详细描述迪帕的研究发现。尽管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这些实验并没有告诉我们,将进口的蚊帐以优惠价出售是否会损害当地厂家的利益),但这些实验结果还是使这场争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极大地影响了这方面的政策导向及言辞。
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入“贫穷陷阱”?
对于蚊帐应免费赠送还是有价销售的问题,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并不是巧合。在发展援助及对待贫穷等问题上,即使一些具体问题似乎应有标准答案,例如蚊帐的价格,但大多数富国专家所持的立场仍会受其特定世界观的影响。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援助机构的参与下)希望能为穷人提供更多援助,免费赠送穷人一些物品(化肥、蚊帐、学生电脑等),我们应劝告穷人去做我们(或萨克斯、联合国)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事。例如,孩子们可以在学校免费用餐,从而鼓励他们的父母定期送他们上学。另一方面,伊斯特利、莫约、美国企业研究院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反对援助,他们不仅认为援助会使政府变得腐败,而且从更基本的层面上看,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们的自由——如果这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理由强迫他们接受:如果孩子们不想去上学,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教育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观点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都是经济学家,他们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个经济问题的回答,即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贫穷。我们知道,萨克斯的观点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佳或运气不好,有些国家陷入了贫穷,而且常常会变得越来越穷。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富裕起来的潜能,却需要先让自身走出困境,然后才能踏上繁荣之路。因此,萨克斯强调巨大推力的重要性。相反,伊斯特利指出,很多过去贫穷的国家现在却很富有,一些过去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变穷了。他表示,如果贫穷的条件不是恒定的,那么“贫穷陷阱”就是一个残酷地诱骗穷国的伪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及个人,人们是否会陷入贫穷?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次性的援助投入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使他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也就是杰弗里·萨克斯“千年乡村计划”所蕴含的根本的哲学理念。在那些幸运的村庄里,村民们得到了免费的化肥、免费在学校用餐及使用计算机、免费的医疗服务等,每个村庄每年消耗50万美元。根据该项目的网站介绍,该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千年村庄经济经过一个时期的过渡,实现了从只够糊口的耕作到自给自足的商业活动的转变”。
在为该计划制作的音乐电视录像中,杰弗里·萨克斯和女演员安吉丽娜·约丽参观了肯尼亚的索里村,这是一座古老的千年村庄。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农民,名叫肯尼迪。由于领取了免费的化肥,肯尼迪家的收成是前几年的20倍,他因此攒下了一些积蓄,足够养活他自己一辈子的了。这里隐含的论点就是,肯尼迪掉进了“贫穷陷阱”,他买不起化肥,免费赠送的化肥解救了他,这是他逃离困境的唯一途径。
然而,怀疑者们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化肥这么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肯尼迪当初为什么不只买一点点化肥,用在那块最好的田地里,这样他就可以提高这块地的产量,然后用挣来的钱多买一点儿化肥,留作来年用。如此循环下去,他就能买下家里田地所需的全部化肥了。
那么,肯尼迪究竟是否掉进了“贫穷陷阱”呢?
答案取决于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一开始只买一点点化肥,多挣一点点钱,然后将收益再次投入,挣更多的钱,最后再重复这一过程。不过,化肥或许只能批量购买,或许在使用过几次之后才有成效,抑或将收益再次投入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你可以想出很多原因,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位农民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发家。
稍后,我们会在第八章深入探讨肯尼迪的故事。但上述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总体的原则:对于几乎无钱可投的人来说,一旦收入或财富迅速增长的范围受限,那么他就会掉入“贫穷陷阱”;但对于有能力投入的人来说,这一范围就会极大地扩展。另一方面,如果穷人快速增收的潜能很大,而且这一潜能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那么“贫穷陷阱”也就不复存在了。
经济学家都喜欢简单(有人称之为单纯化)的理论,他们习惯用图表来表现这种理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为,下列两个图表有助于厘清关于贫穷本质的这场争论。在研究这两个图表时,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即曲线的形状——我们在本书中会多次谈到这些形状。
对于那些相信“贫穷陷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就像图1–1表现的那样,你今天的收入会影响将来的收入,这个将来可能是明天、下个月,也可能是下一代;你今天有多少钱决定着你能吃多少,有多少钱用来买药、支付你孩子的教育费、为自家田地买来化肥或更好的种子,所有这些都决定着你明天会有多少钱。
曲线的形状是关键。这条线一开始很平坦,然后突然升起,之后又逐渐变平。我们暂且选用英文字母“S”为其命名,称之为“S形曲线”。
这条S形曲线就是“贫穷陷阱”的来源。从对角线上来看,今天的收入等于明天的收入。对于处于“贫穷陷阱”地带的穷人来说,将来的收入低于今天的收入:曲线低于对角线。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地带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穷,最终在N点陷入贫穷。从A1点开始的箭头代表一条可能的轨道:由A1到A2,再到A3,如此顺延下去。对于那些起点在“贫穷陷阱”地带以外的人来说,明天的收入会高于今天的收入: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富。以B1为起点、顺着B2、B3延伸的箭头代表着这一可喜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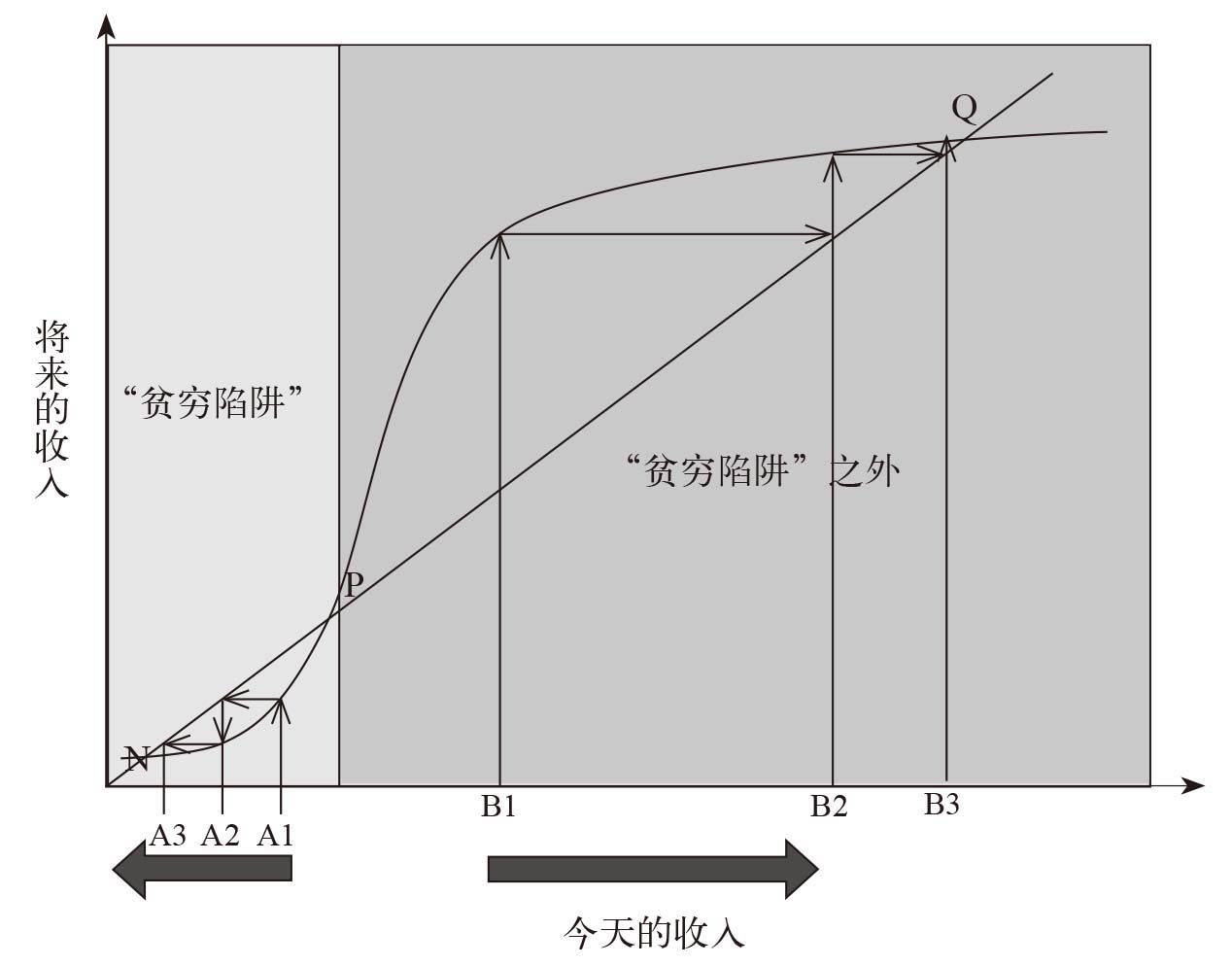
然而,很多(或许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常常更像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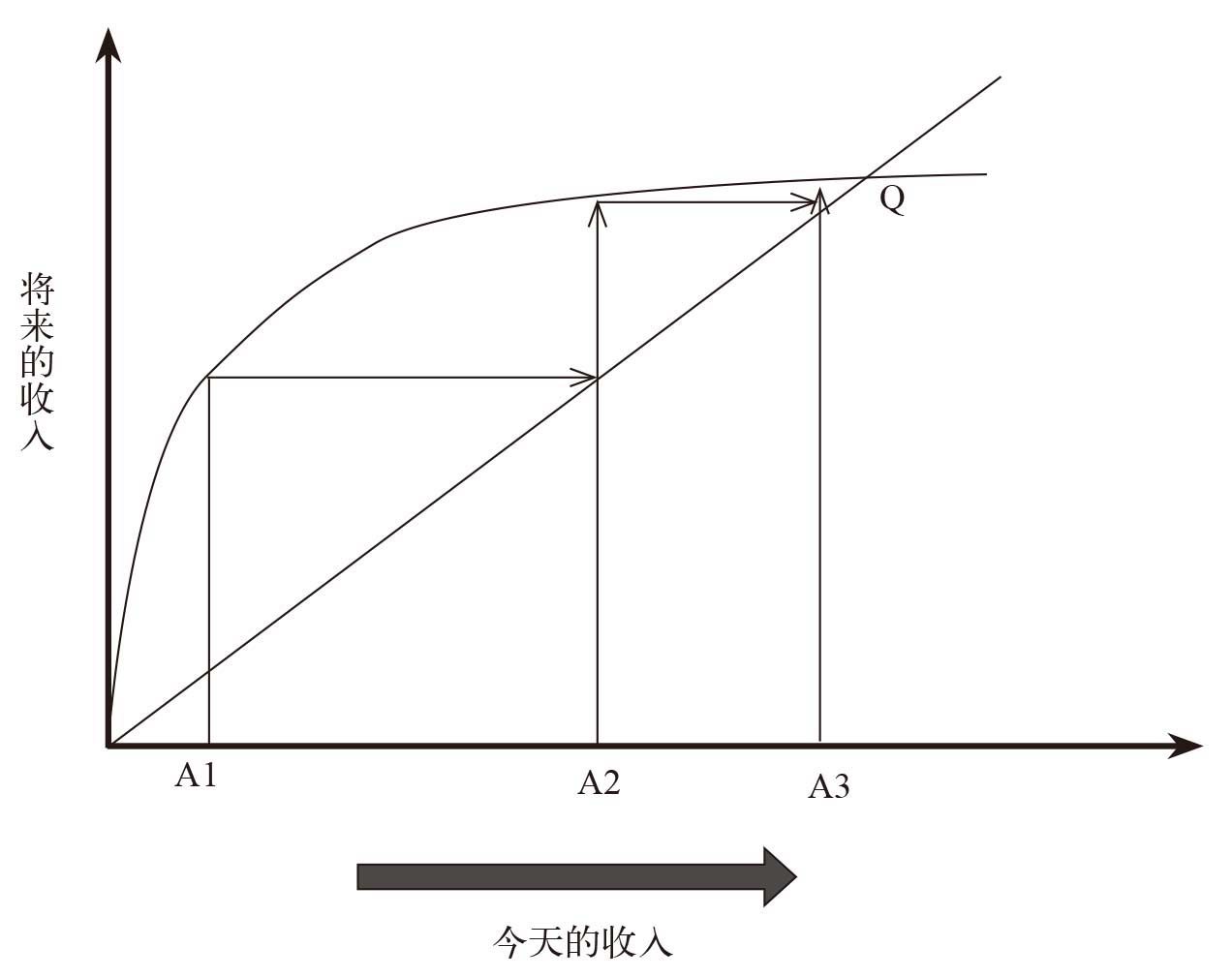
图1–2有点儿像图1–1的右半部分,但它的左端没那么平坦。这条曲线一开始上升得很快,然后慢慢放缓。此图表明,世界上不存在“贫穷陷阱”,因为最穷的人也能挣到比他们原来的收入更多的钱,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富,直到他们的收入停止增长为止(以A1为起点、顺着A2、A3延伸的箭头描绘了这条可能的轨道)。这里所体现的收入或许不是很高,但此图却暗示着,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帮助穷人了。在这个世界上,一次性的施舍(如给某人足够的收入,让她或他以A2而不是今天的A1为起点)并不能永久地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前进得更快一些,并不能改变他们最终前进的方向。
那么,哪个图表能更好地体现肯尼亚年轻农民肯尼迪的生活呢?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一组简单的事实。比如,化肥能否少量购买?一个种植季到下一个种植季期间,是否不太容易攒下积蓄,所以即使肯尼迪在一个季节挣了钱,他也无法用这些钱做进一步投资?因此,这两个简单的图表所包含的理论传达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即仅靠理论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回答“贫穷陷阱”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现实世界能否由图表来体现。而且,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个事例做出判断:如果我们的故事与化肥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关于化肥市场的一些现实情况;如果是关于存钱的分析,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穷人是怎样存钱的;如果是关于营养和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与此相关的领域。找不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这听上去或许会令人有失信心。然而,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想要弄明白的不是穷人陷入困境的100万种方式,而是“贫穷陷阱”形成的几个重要因素。他们想通过缓解特定问题使穷人脱贫,让他们走上一条致富及投资的良性循环之路。
要想放弃那种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就要走出办公室,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传统,即强调通过搜集正确的资料,提出对世界有用的想法。与上一代相比,我们拥有两大优势:第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以前没有的、来自很多穷国的可靠信息;第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强有力的新工具——随机对照实验,使研究人员可以在当地人的配合下开展大规模实验,从而验证他们的理论。在一次随机对照实验中,就像关于蚊帐的研究一样,研究人员随机选定一些个人或团体,让他们接受不同的“待遇”——不同的计划或同一计划的不同版本。由于接受不同“待遇”的个人是具有可比性的(因为他们都是随机选定的),他们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来自特定待遇的影响。
一次实验并不能回答一个计划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行性,但我们可以开展一系列不同的实验,选取不同的地点或实验中不同的外来干预因素(或二者兼有)。统一起来看,我们既可以证实所得结论的可靠性(适用于肯尼亚的理论也适用于马达加斯加吗?),又能缩小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范围(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肯尼迪?是化肥的价格还是钱不容易存的情况?)。这一新理论有助于我们设计一些干预策略及新的实验,使我们弄懂之前可能令我们困惑不解的一些发现。渐渐地,我们就会全面了解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哪些方面不需要帮助。
2003年,我们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鼓励并支持其他研究人员、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致力于采用这种发展经济的新方式,并向政策制定者阐明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人们对此的反响一直都非常强烈。截至2010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已在全球40个国家完成或正在开展240多个实验项目。大量的组织、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都对随机对照实验的想法表示赞许。
人们对实验室研究的反应表明,很多人都赞同我们的基本定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逐步积累、认真的思考、细致的实验与合理的执行,使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许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本书从始至终都会提到,这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常用方式。发展政策的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场争论,似乎都是以证据的不可依赖性为前提的:能被证明的证据是一种妄想,最多只是遥远的梦想,或是一种自娱。当我们开始踏上这条道路时,那些顽固的政策制定者及他们更加顽固的顾问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继续研究,而你们却沉溺于寻求证据。”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不过,还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急促毫无道理可言。他们同我们一样,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困扰穷人的具体问题,尽力找出实行干预的有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并没有一定之规,正如花钱不一定总能解决问题一样。某一特定答案所映射的知识体系,以及对于这些答案的深入了解,才能使我们在某天真正懂得如何消除贫穷。
本书正是建立在这一知识体系之上的。我们所谈到的大量材料,都来源于我们及其他人所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但我们也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一些证据:从质和量的角度描述穷人是怎样生活的,研究一些特定机构是怎样运转的,以及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各类证明。在本书的英文配套网站(www.pooreconomics.com)上,我们提供了相应的链接,读者可以看到书中所引用的各类研究、每一章节的说明图解以及一些摘录和图表,关于18个国家中每人每天不足99美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本书中还会多次提到。
我们所选用的研究都有共同点,即表现了科学的强大力量、接受有关资料结论的开放性,以及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这些资料将表明,我们应在何种情况下担心陷入“贫穷陷阱”——“贫穷陷阱”并不是存在于每个领域。要想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我们有必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错误的政策是怎样制定的,这种政策并非来自动机不良或是腐败,而仅仅是因为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世界模式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有“贫穷陷阱”,而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另一个“贫穷陷阱”就摆在他们眼前,却被他们忽略掉了。
然而,本书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贫穷陷阱”。我们将会看到,专家、援助者及当地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无知及惯性常常可以表明,为什么有些政策失败了,有些援助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我们能够将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可能无法在明天就实现,但一定会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将来实现。不过。靠惰性思维是无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一步步耐心的研究,不仅仅是抗击贫穷的有效方式,而且还能使世界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
对 于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除了2004年12月的大海啸和2010年海地地震这种大天灾之外,最能影响全球穷人的事件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以及1985年3月举行的“天下一家”音乐会。该事件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催生了大规模的慈善活动。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这一说法的影响力颇大,超过了世界银行对全球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人数的统计。
贫穷与饥饿已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其表述方式为,“消除贫穷与饥饿”。的确,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贫穷线,其最初的依据就是饥饿的概念、购买一定量食品的预算,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支出(如住房)。“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因此,政府对穷人的大力救助势必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穷人迫切地需要食物,而需求量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食品补贴在中东司空见惯:埃及在2008—2009年花费了38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食品补贴;印尼制定了分配补贴大米的Rakshin计划;印度的很多邦都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例如,在奥里萨邦,穷人每月可以购买55磅大米,每磅4卢比,这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20%。目前,印度议会正在就构建《食品权利法案》展开辩论,这一法案将赋予人们因挨饿起诉政府的权利。
就物流方面来说,大规模的粮食援助如噩梦一般。据估计,印度超过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米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都被老鼠糟蹋了。如果政府漠视这种浪费,仍坚持原有政策,其原因或许是他们认为饥饿与贫穷之间联系紧密,还可能因为人们觉得,穷人没有能力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也是“贫穷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曾向我们解释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房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民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民决定不削减工资,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如果年轻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通常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解释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经验,对于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介绍,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够养活三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尽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另外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济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游泳)。他的弟弟偶尔也会救济救济他。就在我们跟他谈话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顿。
帕克的情况似乎让他别无选择,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粮食问题,或者更确切点儿说,是缺粮问题。他认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之所以决定辞退工人,而不是降低工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在粮食涨价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会让工人吃不饱饭,降低他们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效率。这正是自己找不到活儿干的原因。显然,他愿意找活儿干,但由于吃不饱,他整个人都虚弱无力,沮丧之情随之而来,这也在一点点削弱他的意志,使他不再去想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帕克的经历来看,“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人们能否获取足够的营养,但这一概念却是老生常谈。早在1958年,经济学中就已首次出现这一正式说法。
这个概念的道理很简单。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能量。如果一个人穷困潦倒,那么即便他倾其所有,也仅够买果腹之食,勉强维持生命而已。我们遇到帕克时,他的情况就是如此:忍饥挨饿,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只能用来到河里捕鱼。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满足,所有额外的食物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满足维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这一简单的生理机制产生了今天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图1–1所展现的情况:穷人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向我们解释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因素,尽管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苏丹见到他的,也不是在洪灾肆虐的孟加拉国,而是在富裕城市爪哇的一个村庄。那里的粮食价格尽管在2007—2008年有所上涨,但当地的粮食储备显然是充足的,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当我们见到帕克时,他显然吃不饱,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花钱雇用他,给予他所需的额外营养,使他具备足够的生产力,然后让他来干一整天的活儿?“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饥饿这种看法虽然颇具合理性,但在实际情况中,就今天的大多数穷人来说,“贫穷陷阱”与饥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人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人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余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其他必需品上。比如,在印度的乌代布尔,我们发现,如果完全去除烟酒及节日性花费,一般的贫困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钱比实际多30%。穷人似乎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并不推崇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吃的。
看看穷人会怎样花掉偶尔多出来的钱,这一点便显而易见。尽管他们会首先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花费(他们需要衣服、药品等)。如果他们的谋生方式主要依靠体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手头有了一点儿多余的钱,他们也会全部用来买吃的,其食物预算的比例也会比整体预算上升得快(因为二者上涨的量是相同的,而食物只是整体预算的一部分,因此其增长的比例更大)。然而,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正确。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1983年时(距离印度近期的发展还很遥远——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即使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在1%的总体花费中,有67%都花费在食物上。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一事例中最贫穷的人(每人每天约挣50美分)和最富有的人(每人每天约挣3美元)来说,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例子中,全球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即使对于十分贫穷的人来说,食物花费的上涨也远远低于原来的预算。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当穷人可以多买一点儿食物时,他们并不注重用所有投入换取更多能量。相反,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价钱更高的食品。对于1983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工资的上涨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但人们却用50%的工资来购买能量更高的食品,另外50%则用来购买价钱更高的食品。就每个卢比所购买食品的能量来说,小米(高粱和珍珠粟)显然是最合算的。然而,人们只用约2/3的钱购买了这种粮食,另外1/3的钱买了大米和小麦(其提供每卡路里热量的价钱约为小米的2倍)。此外,穷人用来买糖的钱几乎占其总预算的5%,同谷物相比,作为人体能量来源的糖价格更高,但其营养价值却远远不及谷物。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那些得到补贴的人来说,尽管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但其自身的能量吸收并没有提高,而且可能还会有所降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人所摄入的营养含量也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主食占家庭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补贴使他们变得更富有:如果主食的消费与贫穷的状态有关(比如说,因为主食价格便宜,但不那么好吃),那么富有的感觉可能会促使他们买更少的主食。这再次表明,至少对于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在今天的印度,营养问题也成了一个谜。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标准报道就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肥胖及糖尿病病例呈快速增长之势。然而,安格斯·迪顿和让·德雷兹表示,过去25年来,印度人的营养问题并不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是他们实际上吃得越来越少。尽管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其人均卡路里消费却在持续下降。此外,除了脂肪之外,各类人群(即使是最贫穷的人群)在其他营养品上的消费似乎也有所下降。迄今为止,城市地区超过3/4的人口人均卡路里消费不足2 100卡,农村地区人口则不足2 400卡——印度将这组数据作为体力劳动者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富人比穷人吃得更多,这仍然是一个现实情况。然而,从各个收入水平来说,用于购买食品的预算部分已有所下降。而且,食品的构成已然改变,同样数目的钱现在被人们用来购买了价格更高的食品。
这一变化并非源于收入的下降——据某些人说,实际上收入正在增长。虽然印度人现在越来越富有,但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却吃得比以往更少。原因也并不在于食品价格的上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05年期间,无论是在印度的农村还是城市,食品价格较之其他产品都有所下降。虽然食品价格自2005年起再次上涨,但卡路里消费的下降正是发生在食品价格下降之际。
因此,包括被世界粮农组织归类为饥民在内的穷人,即使在可以吃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也不愿意那样做。的确,他们似乎吃得越来越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揭开这一谜团的合理起点是,假定穷人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毕竟,他们是能吃能干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吃得更多,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挣到更多的钱,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他们便会抓住。因此,是否吃得更多并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
“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 700卡路里热量。这是几个世纪粮食供应革新的成果,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农业科技领域的伟大革新,还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吃得比所需的多,或者更合理地讲,将更多的玉米转化成了能量,我就能好好游游泳,那么所有其他人得到的就会更少。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根据菲律宾人的价格数据,我们算出了足以提供2 400卡路里的最便宜食品的价格,包含10%来自蛋白质的卡路里,还有15%来自脂肪的卡路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只会花费21美分,就算是每天靠99美分生活的人也买得起。问题在于,这样,他们只能吃到香蕉和鸡蛋。不过,只要人们在必要时有吃香蕉和鸡蛋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停留在S形曲线的左半边,这说明他们都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
这与印度的调查结果一致。在那些调查中,人们需要回答,他们是否能吃饱,比如,“每个家庭中的每个人一天吃两顿饱饭”,或者“每人每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认为自己吃不饱的人,其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减少——从1983年的17%降到2004年的2%。因此,人们之所以会吃得更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饥饿程度降低了。
或许,尽管人们摄入了更少的卡路里,但他们真的不再那么容易饥饿了。或许,由于水质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因一次次的腹泻或其他疾病而流失那么多卡路里。或许,人们的饥饿程度之所以降低,是因为重体力劳动的减少——村里有了可饮用水,妇女们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地去挑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们出门就不用全靠步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村子里,面粉都用电动磨粉机来磨,而不是由妇女们用手来磨。印度医学研究会分别计算了重度、中度及轻度体力劳动者的卡路里需求量,通过计算出来的卡路里平均值,迪顿和德雷兹注意到,过去25年来,卡路里消耗量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
如果大多数人都处于非饥饿状态,那么他们因消耗更多卡路里而获取的生产力就可能相对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把钱花在别处,即放弃香蕉和鸡蛋,转而选择某种更棒的食品。很多年前,约翰·施特劳斯为证明卡路里对生产力的作用,一直在寻找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选定了塞拉利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是真正辛苦劳作的人。约翰发现,如果一个农工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0%,那么他的生产力最多可以提高4%。因此,即便人们加倍消耗食品,他们的收入也只能增加40%。此外,卡路里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呈S形曲线,而是反向的L形曲线,就像图1–2所展现的那样:最高的收入来自低水平的食品消耗。一旦人们能够吃饱饭,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表明,与不那么贫穷的人相比,摄入更多卡路里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更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恰恰看不到所谓的“贫穷陷阱”。因此,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并非是由他们吃不饱饭造成的。
这并不是说,基于饥饿的“贫穷陷阱”存在不合理性。更丰富的营养可以使某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想法从历史角度来看的确至关重要,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要。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时期,粮食产量并不足以维持所有劳动者所需的卡路里,这就是当时出现大量乞丐的原因——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仅仅是糊口的压力,似乎就足以迫使某些人采取极端的做法: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时期,曾盛行“杀死女巫”活动。当时农作物歉收的现象十分普遍,渔业也不发达。女巫们大都是单身女性,其中以寡妇居多。S形曲线的逻辑表明,当资源紧缺时,通过牺牲某些人,让余下的人能吃饱,使其具备劳动能力,为生存而赚钱,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贫穷家庭偶尔会被迫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至今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旱灾期间,很多家庭无地可种,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夭折,但在雨水正常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死亡比例并无多大差别。而在“小冰期”时期,坦桑尼亚一旦发生旱灾,就会经历一次“杀死女巫”的暴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是除掉无用闲人的一种便捷方式。很多家庭会在突然间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较年长的女人(常常是祖母)是一个“女巫”,然后她就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追捕或杀死。
因此,粮食短缺有时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都十分富裕,关于贫穷的故事并不会成为它的主旋律。不过,在天灾人祸频发时期,或是当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去或病倒时,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现有食品分配不合理,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将可用粮食储存起来。
那么,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我们能否考虑到,尽管穷人可能吃不了多少,但他们仍需要吃饱。
我们始终感觉,与真实情况相比,任何故事都欠缺说服力。假定在印度最贫穷的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1 400卡路里,会有人因不需要那么多卡路里而减少食品消费吗?1 200卡路里是众所周知的半饥饿状态,想要快速减肥的人常会得到这样的饮食建议;不过,1 400卡路里似乎比这种状态强不了多少。据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称,2000年美国普通男性每天消耗2 475卡路里。
然而,印度最贫穷的人的身材较为瘦小,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如果一个人身材十分瘦小,那么她/他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卡路里。不过,这是不是又把问题推回原地了?为什么印度最贫穷的人身材如此瘦小?为什么南亚人都骨瘦如柴?衡量营养状态的标准方式是体重指数(BMI),这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重要方式(如身高更高的人体重也就更重)。营养不良的国际底线为BMI 18.5,BMI在18.5~25之间属于正常范围,BMI超过25的人被定为肥胖状态。通过这一衡量标准,2004—2005年间,印度33%的男人和36%的女人是营养不良的,二者在1989年时的这一比例均为49%。在提供人口统计及健康调查数据的83个国家之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出现了更多营养不良的成年女性。印度女性、尼泊尔女性及孟加拉国女性,也属于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女性。
这一点是否应加以考虑呢?这是否应完全归因于南亚人的基因问题,就像深色眼睛或黑色头发一样,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否无关?毕竟,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的南亚移民,他们的孩子也比白人孩子或黑人孩子个子更矮。然而,在无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代人一直生活在西方,南亚移民的孩子在身高上便会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差不多。因此,尽管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基因构成的确至关重要,但人类在身高方面的基因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如果第一代母亲的孩子身材依然十分矮小,那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母亲在童年时就营养不良,因此才会生下身材较为矮小的孩子。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南亚人身材矮小,很可能是因为南亚人及其父母所吸收的营养较少。有证据表明,印度的儿童极度营养不良。衡量儿童在童年时期是否营养充足,常用的尺度就是对照这一年龄的国际标准身高。通过这一标准,印度国家家庭卫生研究(NFHS)所显示的数据令人震惊:约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营养摄入还远远达不到标准。其中1/4的孩子极度营养不良,说明儿童营养问题的严重性。参照孩子们的身高,他们的体重也大大低于标准体重:在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处于消瘦状态,也就是说,低于国际极度营养不良的标准。令人尤为震惊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那里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的比例,仅为印度的一半。
对此,我们是否应在意呢?这本身不就是个小问题吗?那么,别忘了还有奥运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48.3枚。世界上72个国家的奥运会成绩都优于印度,除掉其中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印度的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人口的10倍。
印度虽然是贫穷国家,但它并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而且还要好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及乌干达。然而,这些国家人均获奖数却是印度的10倍以上。的确,每届奥运会获奖数少于印度的国家,其人口几乎都不到印度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从未获过奥运会奖牌的国家,尼泊尔次之。
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有人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南亚人对于板球的沉迷——这也是一种殖民产物,与困扰美国人的棒球相伴生——但就算板球占据了世界1/4人口所有的运动才能,它在奥运会上的弱势便情有可原了吗?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小小的西印度群岛都热衷于体育,而且还占据人口上的优势,但南亚人从未像这些国家在其繁荣期那样,统治过板球这一领域。例如,孟加拉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印度群岛的总和。鉴于儿童营养不良是南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儿童发育迟缓和奥运会成绩不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奥运会并非唯一一个身高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身材高大的人都能挣得更多。关于身高是否与生产力相关,人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莫衷一是。比如,有人争辩说这种说法歧视身材较矮的人。然而,安妮·凯斯和克里斯·帕克森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身高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智商的高低完全可以由身高的效应来解释:但当我们对智商相同的两个人做比较时,身高与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为了解释这一发现,凯斯和帕克森表示,真正起作用的是童年时期充足的营养摄取。一般来说,童年摄取充足营养的人,都会长得更高大、更聪明。正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所以他们才会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很多不那么高大的人也很聪明(因为他们已长到应有的高度),但总体来说,个子高的人在生活中更出色,因为他们显然更可能发挥自身的遗传潜力(在身高及智力方面都是这样)。
路透社将这项研究以《关于更高的人更聪明的研究》为标题做了报道,听上去很平常,却引发了一场风暴。凯斯和帕克森顿时淹没在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之中。一个男人(身高1.5米)责备说,“你们太可耻了”;另一个人(身高1.71米)说道,“我觉得你们的结论具有侮辱性、煽动性,是一种偏见和偏执”;还有一个未透露身高的人说,“你们拿了一把枪,将枪口对准了个子不高的人群的脑袋”。
然而,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一些最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入具有深远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营养不良会影响人们未来的生活机遇,这种影响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首次使用了“巴克假说”(Barker Hypothesis)一词,这是戴维·巴克医生的理论,即母体子宫的条件对婴儿生活机遇具有长期影响。很多人都支持“巴克假说”。例如,在坦桑尼亚,与未服用碘胶囊的孕妇所生的孩子相比,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了足够量的碘(根据一项间歇性的政府计划,政府会向孕妇发放碘胶囊),她们生下的孩子能够多上4个月至半年的学。尽管多上半年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考虑到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只能上四五年学,多上半年学就意味着不小的收获。实际上,在这一估算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每位母亲当初都服用了碘胶囊,那么非洲中部及南部孩子们的学习总成绩就会上升7.5%。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孩子们一生的工作能力。
尽管我们看到,单凭卡路里的增加,本质上对生产力似乎没多大影响,但即使成人也有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方法。我们熟知的一种方法就是,多吸收铁元素可以治贫血。在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贫血都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印尼6%的男性和38%的女性都患有贫血症,印度的相应数据为24%和56%。贫血与有氧代谢能力低下、身体虚弱及疲倦有关。在某些病例中,特别对于孕妇来说,贫血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印尼的铁营养状况评价与研究项目在农村随机选出一些男性和女性,每几个月定期为他们补充铁元素,给另一对照组用的则是安慰剂。研究表明,铁元素的补充使男性工作更努力,他们由此而增加了收入,可以用来买几年所需的加铁鱼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购买一年的鱼酱只需花费7美元。如果是一位男性个体户的话,他补铁后每年的收入会增加46美元——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问题是,人们似乎不想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特别是更多理智购买的食物,可以使人们及其子女在生活中更成功。而且,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投资并不昂贵。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剂药花费51美分)。在肯尼亚,国际儿童扶持会制订了一个抗蠕虫计划,呼吁家长为他们正在上学的孩子花上几美分,接受抗蠕虫治疗。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没有响应,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一生多赚上百美元的机会。至于食物方面,各个家庭只需少买一点儿昂贵的谷类粮食(如大米和小麦)、甜食及加工食品,多买一点儿叶类蔬菜及粗粮,就会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卡路里及其他营养物质。
为什么贫血的印尼上班族自己不买加铁鱼酱?一种答案就是,如果老板们意识不到营养充足的员工工作能力更强,那么员工自然会对“更强的工作能力将获取更多的收入”产生怀疑。如果老板付给每位员工相同的工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吃得更多、变得更强壮了。在菲律宾,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既要挣基本工资又要挣计件工资的人,他们在挣计件工资时要多吃25%的食物。在挣计件工资时,工作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干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所有的怀孕妇女都不吃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几乎在每个村子都能买到。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有什么价值。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一样,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善。尽管微量营养素价格便宜,而且有时能够大大提高人们一生的收入,我们仍然有必要搞清楚该吃些什么(或该服用哪种药)。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即使是在美国也一样。
此外,当别人告诉自己应改变饮食结构时,人们一般都会持怀疑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钟爱自己吃的食物。1966—1967年时,大米的价格迅速上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说,少吃大米多吃蔬菜不仅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节省他们的预算。这引发了一阵阵抗议。于是,这位部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蔬菜做的花环迎接他。现在看来,他或许是对的。安托万·帕芒蒂埃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药剂师,早年十分热衷于土豆。不过,安托万了解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他显然已经预见到了人们对此所持的反对意见。他向大众展示了一套他自己发明的土豆食谱,包括经典菜——帕蒙蒂耶烤土豆泥(Hachis Parmentier),英国人将其称为“羊倌肉饼”,是由一层碎肉和一层土豆泥做成的焙盘。于是,安托万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迂回曲折,但最终,他发明了“自由薯条”。
另外,仅凭个人经验,并不容易了解太多这种营养物质的价值。碘会使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但摄入量的多少并无多大差别(不过,量变也会引起质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多年之中既不会发现小变化,也看不到大变化。碘虽然能使人变得更强壮,但并不能突然之间把你变成一个“超人”——个体户每周的收入都会出现上下波动,因此对他自己来说,每年多挣40美元也可能察觉不到。
因此,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乔治·奥威尔在其《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一书中,成功地描述了英国穷人的生活。书中写道:
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如果他们多花点儿钱,去买一些健康食品,如橘子和全麦面包;或者,他们可以学《新政客》(New Statesman )的读者,为节省燃料而生吃胡萝卜,那样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样当然会更好,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样做。还没等到要靠黑面包和生胡萝卜为生时,正常人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了。而且,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
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穷人饮食习惯的另一个解释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印度婚礼的花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场合,如一个家庭被迫举办一场奢侈的聚会。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婴儿出现死亡的时期,人们制定了葬礼应花多少钱的社会规范。根据传统,人们只需将死去的婴儿简单埋葬,但要为死去的老人举办隆重的葬礼,葬礼所需费用为死者一生的积蓄。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费用,便要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即使死者生前没有挣过钱,情况也是一样的。这表明,葬礼的花费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葬礼所花的钱越多,人们来年就会变得越沮丧,而他们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辍学。
因此,无论是瑞士的国王,还是南非基督教协会(SACC),都在努力调整葬礼的支出,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2002年,瑞士国王发布禁止葬礼铺张浪费的条令,宣称如果发现哪个家庭为办葬礼而宰了一头牛,他们必须再上交一头牛。南非基督教协会则表现得更加严厉,他们呼吁整顿葬礼产业,认为这是在向那些入不敷出的家庭施加压力。
然而,将钱花在食品以外的地方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压力。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就连帕克·索林都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我们见到他时,那台电视机出了毛病。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穷人要常常进行某种特别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人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况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农村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花钱。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今天,电视信号可以覆盖一些偏远地区,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人们也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移动电话几乎无处不在,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话费还特别便宜。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十分繁荣,大量消费品也都很便宜(比如印度和墨西哥),但这些国家的食品消费却是最低的。印度的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个小商店,大多数情况下会有好几个,在那里可以买到袋装的洗发液,按支销售的香烟,便宜的梳子、钢笔、玩具或蜡烛;而在像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食品消费占每个家庭预算的70%以上(在印度是50%),穷人们能买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少。这一现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人是怎样逃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我们以帕克·索林及其观点开启这一章,他认为自己陷入了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从表面上看,他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卡路里。Rakshin计划使他得到了一些免费的大米,他的兄弟有时也会帮帮他。在其他时间里,他应该有体力到田间或建筑工地干活儿的。我们对相关证据的解读表明,大多数成年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是处于“贫穷陷阱”地带之外的:他们很容易就能吃够干好体力活儿所需的食物。
帕克·索林的情况或许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陷入贫穷,问题可能在于他失去了工作,而且他的年龄太大,已不适合再到建筑工地当学徒。此外,他的沮丧无疑使他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不适用于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在营养方面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缺失。营养充足可能会为两类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即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因为他们还不能自主选择食物。实际上,父母收入与其子女未来收入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种S形曲线关系,这与子女在童年期间的营养摄入有关。这是因为,如果孩子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那么他/她以后每年都会挣到更多的钱:经过一生的积累,这个孩子就会受益匪浅。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肯尼亚对儿童做抗蠕虫预防,我们对其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两年而非一年治疗的儿童(因此其两年来的营养状态更好)一生收入为购买力平价3 269美元。童年时期营养上的小投入会在以后产生大影响(在肯尼亚,抗蠕虫每年花费购买力平价1.36美元;在印度,一包碘盐价格为购买力平价0.62美元;在印尼,加铁鱼酱价格为购买力平价7美元)。这表明,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粮食那么简单,尽管大多数食品安全计划目前都着意于此。穷人喜欢补贴的粮食,但我们前面谈到过,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并不能使他们吃得更好。而且,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在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成分。此外,仅仅靠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正如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和欲望。
相反,对儿童及孕妇的直接营养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向孕妇及儿童父母发放强化食品,对儿童进行学前或在校的抗蠕虫预防,向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或者鼓励父母为补充营养而消费。在有些国家,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得到实行。肯尼亚政府目前对在校儿童提供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哥伦比亚政府会在学前孩子的膳食中加入微量营养素;在墨西哥,社会福利机构为家庭提供免费的营养补充。食品技术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人们喜爱的食物中加入额外的营养素,生产出一些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适于在各类环境中种植的新品种粮食,同时还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在世界各地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实例,其推动者都是国际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Micronutrient Initiative)和国际农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等机构。近期,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引进了各类适合非洲的橘子味土豆(β–胡萝卜素更丰富)。目前,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已批准使用一种富含铁和碘的新型食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食品政策只停留在这样一种想法上,即穷人需要的只是便宜的粮食。
健 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会给人带来失望。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从疫苗到蚊帐,都是一些低成本却可以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性措施。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医务人员负责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但他们常常因不称职而受到责备。我们会看到,这种责备也不无道理。而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坚持认为,那些“好摘的果子”比看上去难摘多了。
2005年冬,在印度西部美丽的乌代布尔城,我们与一些政府医疗机构的护士进行了一次气氛活跃的交谈。她们对我们非常失望,因为我们谈到的项目会加大她们的工作量。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其中一位护士忽然发起了脾气,她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工作其实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曾经有个患痢疾的小孩来看病,护士们能给孩子母亲的只有一盒口服补液 [1] 。然而,大多数母亲都不相信口服补液可以治病,她们想得到自己认为能够治病的药——一剂抗生素或一次静脉注射。护士们告诉我们,一旦一位母亲从医疗所拿走的是一包口服补液,那么她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每年,护士们都会看到很多儿童死于痢疾,但她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在每年900万死于5岁前的儿童中,大多数来自南亚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而且约每5名儿童中就有一个死于痢疾。相关部门正在努力开发并分发一种抗轮状病毒的疫苗,轮状病毒是一种能引起痢疾的病毒。然而,已经有三种“神药”可以挽救大多数儿童的生命了,即用来净化水的消毒剂,还有糖和盐(口服补液的主要成分)。只需用100美元购买一个家用氯包,就能够预防32个痢疾病例。脱水是痢疾致死的一个主要病因,而口服补液是一种可以有效预防脱水的药。
然而,无论是消毒剂还是口服补液,都未被广泛使用。在赞比亚,由于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 International,简称PSI)的努力,消毒剂的价格很便宜,而且已得到了广泛使用。PSI是一家专门在全球以补贴价格销售消毒剂的大型组织。只需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为0.18美元),一个6口之家就能够买到足够的消毒剂,用于净化水源,这样他们就不会因水传播而患上痢疾。不过,只有10%的家庭使用消毒剂。在印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称,在5岁以下的儿童痢疾患者中,只有1/3服用了口服补液。痢疾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通常用开水、糖和盐就能进行治疗,那么为什么每年还有约150万儿童死于痢疾呢?
消毒剂和口服补液并不是什么特例,还有其他相对“好摘的果子”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挽救很多生命。那些方法简单、廉价,如果恰当地利用,就能够节省大量资源(如减少额外工作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增强体质等)。除了挽救生命,这些方法还可以为自身买单。然而,太多这种“果子”都未被摘下。并非人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他们只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比如,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抗生素、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印尼的一个村庄,我们遇见了伊布·艾姆塔特,一位竹篮编织工的妻子。2008年夏天,她的丈夫因眼睛有点儿问题而不再工作。伊布没有办法,只好借了4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74.75美元),10万用来为她丈夫买药治病,30万用于在她丈夫恢复期间购买食品(她7个孩子中的3个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每月要为贷款支付10%的利息。然而,当我们见面时,他们欠下的利息越来越多,已经积累到1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7美元);于是,放债人威胁说要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她的小儿子最近被诊断患了严重哮喘。由于这个家庭已经债台高筑,她已经拿不出钱为儿子买药治病了。我们拜访时,这个孩子一直和我们坐在一起,每过几分钟就会咳嗽一次;他已经不能再按时上学了。这个家庭似乎掉进了一个典型的“贫穷陷阱”之中——父亲的病使他们陷入了贫穷,导致孩子的病没钱治,从而耽误了上学,他的未来也因此笼罩在贫穷的阴影之下。
健康确实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工人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儿童可能会因病无法正常上学,孕妇可能会生下不健康的婴儿。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当前的不幸转化成未来的贫穷。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只需要努力一把,就可以让一代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成长、工作,将他们从陷阱中解救出来。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或整个国家,都掉进了一个健康陷阱之中。他常常以疟疾为例,有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受到了疟疾的影响,这些都是较为贫穷的国家(平均来说,在科特迪瓦或赞比亚这样的国家,受疟疾影响的人口占50%或以上,人均收入仅为无疟疾病例国家的1/3)。而且,正因为如此贫穷,这些国家采取疟疾预防措施的难度才会更大,从而导致其一直贫穷下去。然而,据萨克斯称,这也意味着,在这些国家进行旨在控制疟疾的公共健康投资(如分发蚊帐,使人们在夜间远离蚊虫的困扰)将会产生很高的回报:人们得病的概率会减小,工作会更加努力,收入会因此而增加,足以用来支付这些外来投资。从第一章中S形曲线的角度来说,受疟疾困扰的非洲国家都位于曲线的左半部分,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因疟疾而身体衰弱,工作效率极低。因此,这些国家没有消除疟疾所需的资金。不过,如果有人出资抗击疟疾,那么这些国家最终就会移到曲线的右半部分,走上繁荣之路。同样,这一理论也适用于贫穷国家的其他多发疾病,这就是萨克斯《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一书中所传达的乐观信息的核心。
怀疑者们很快指出,目前尚不清楚那些滋生疟疾的国家贫穷的原因是否在于疟疾,就像萨克斯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这些国家无力消除疟疾,也许只是说明它们的管理能力很差。如果是后一个原因,那么除非改善管理体制,否则仅仅靠消除疟疾,或许还不能完全解决贫穷问题。
现有证据究竟支持谁的观点?活跃分子还是怀疑者?我们对多个国家成功抗击疟疾的案例进行了研究,每份研究都对该国疟疾高发地区与低发地区进行了对比,并对抗疟活动前后出生于该地区的儿童进行了检查。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那些疟疾高发地区,出生于抗疟活动之后的儿童与出生于疟疾低发地区的儿童相比,二者的人生成就(例如教育或收入)是基本一致的。这有力地表明,消除疟疾的确会减少长期贫穷现象的发生,尽管效果不像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那样大。一项针对美国南部(1951年之前一直受疟疾困扰)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抗疟活动的研究表明,与患过疟疾的儿童相比,未患过疟疾的儿童长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类似的研究结果还出现在印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不过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国家而异。
这一结果表明,投资预防疟疾的经济回报可能会非常高。在肯尼亚,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最多花费14美元,而效力却达5年之久。我们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一个肯尼亚儿童从出生到2岁一直睡在这种蚊帐中,那么他较之其他儿童感染疟疾的概率会减少30%。在肯尼亚,成年人的年均收入为购买力平价590美元。因此,如果疟疾真的会减少肯尼亚50%的收入,那么14美元的投资将会为30%人口增收295美元,而如果没有蚊帐,这些人就可能会感染疟疾。儿童成年后的全部工作时间每年都会带来88美元的收益——足够每个家长为其子女买一辈子的蚊帐,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还有很多其他高效健康投资的例子,可用纯净水及公共卫生就是其中之一。总体来说,根据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约13%的世界人口缺乏改进的水源(通常指自来水或水井),而约1/4的人口没有可用的安全饮用水,其中有很多都是穷人。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中,在农村极度贫穷的人口中,具备家用自来水条件的人口比例为1%(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农村)到36.8%(危地马拉)不等。虽然情况因国而异(就农村中产阶层来说,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低于3.2%到巴西的80%),但对于更富裕的家庭来说,这一比例一般会更高。此外,无论是穷人还是中产阶层,城市地区的这一比例都会较高。在穷人的世界里,良好的卫生设施简直少得可怜——世界上42%的人口没有家用卫生间。
大多数专家一致同意,家用自来水及卫生设施会给健康带来很大影响。一项研究表明,由于自来水、良好的卫生设施及水源氯化的推广,1900—1946年间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约3/4,使同期死亡率总体减少了几乎一半。此外,童年期间的痢疾复发会永久伤害孩子的身体及认知上的发育。据估计,通过用管道向家庭输送无污染的氯化水,痢疾病例可减少95%。劣质水和死水也是其他主要疾病的一个来源,如疟疾、血吸虫病及沙眼,这些疾病都可能导致儿童死亡,或降低他们长大后的工作效率。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每月花费20美元用于支付自来水及卫生设施的费用,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太贵了。印度奥里萨邦的格莱姆维卡斯是一家非政府组织,它认为,可以通过更廉价的方式取得这一成果。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乔·马蒂斯是一个性格幽默的人,做事习惯于另辟蹊径,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富豪年会时,他穿了一身手织的棉布衣服。马蒂斯很早就是一名社会活跃分子,12岁时就组织工人到他父亲的农场抗议。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就同一群左翼学生一起来到了奥里萨邦,参加一场龙卷风大灾后的救援工作。在紧急救援工作结束之后,为了帮助奥利亚村贫穷的村民,他决定留下来,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更持久有效的办法。最终,马蒂斯决定从改善水和卫生条件做起。这一问题既是一个日常难题,也是他开启长期社会变革的一次机会。他在奥里萨邦向我们解释说,水及卫生设施是社会问题。马蒂斯坚持认为,在格莱姆维卡斯负责的所有村子里,每个家庭都应该与一个总水管连接,再通过管道将水输送到每个家庭,包括由同一系统连接的卫生间、水龙头及浴室。对于上层阶级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与下层阶级家庭分享水源。在这一想法刚刚提出时,奥里萨邦的很多人都无法接受。非政府组织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一个村子全体村民的同意,而有些村子最终还是拒绝了。不过,非政府组织所坚持的一贯原则就是,除非得到一个村子所有村民的同意,否则他们是不会在那里开展工作的。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有些上层阶级家庭首次参与了这种由一个社区所有人参与的活动。
一旦一个村子同意配合格莱姆维卡斯的研究,为期一两年的建筑施工就会启动。只有在每个家庭都配好自来水及卫生间之后,这个系统才会开始运转。同时,对于每月来卫生所治疗疟疾或痢疾的人,格莱姆维卡斯都会收集他们的信息。这样一来,只要水流动起来,该组织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一个村子的情况。结果证明,效果十分显著:几乎一夜之间,痢疾重症病例减少了一半,疟疾病例也减少了1/3,而且这一效果能持续好几年。每个家庭每月为此支付的费用(包括维护费用)为190卢比(现价为4美元),仅为这种系统正常价格的20%。
当然,避免痢疾还有更廉价的方法,如在水中加入消毒剂。其他廉价而有效的医用或公共卫生方法包括发放口服补液、给儿童接种疫苗、发放抗蠕虫药剂、婴儿出生6个月之内由母乳喂养;还有一些常规的孕期保健方法,如给孕妇打破伤风针,发放防夜盲症的维生素B、防贫血的铁片及加铁面粉等,这些都是“好摘的果子”。
能够找出这些方法,都要归功于杰弗里·萨克斯的乐观与耐心。在萨克斯看来,有一种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但我们可以向穷人提供“梯子”,帮他们逃离这些陷阱。如果穷人买不起梯子,那么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会伸出援手。这也是格莱姆维卡斯在奥里萨邦所做的,帮助村子进行管理、补贴水系统的花费等。几年前,乔·马蒂斯告诉我们,当发放官坚持要村民将受赠物品全价买下时(幸运的是,该基金会随后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觉得自己必须拒绝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资助。马蒂斯称,虽然健康福利潜在的价值的确很大,但村民们每月根本拿不出190卢比——格莱姆维卡斯只是要村民们向村基金会支付一定数量的钱,使村里的水系统得到良好维修,并可以随着村子的发展而服务于更多的家庭。至于其余的必要款项,非政府组织会从世界各地的捐赠者那里筹集。萨克斯认为,这才是合理的方式。
然而,萨克斯的理论存在一个缺陷,即穷人处于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之中,用钱就可以把他们救出来。其中有些方法十分廉价,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都负担得起。例如,母乳喂养根本无需任何花费。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有不到40%的婴儿得到了6个月的母乳喂养。再以饮用水为例,我们看到,通过管道将水输送至各个家庭每月花费190卢比(包括排污费用),也就是每年2 280卢比。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30万克瓦查。不过,贫穷的赞比亚村民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然而,只需拿出这笔钱的2%,一个赞比亚的6口之家就能够买到足够的消毒剂,用于净化他们全年的饮用水: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经销的一种品牌的消毒剂只需花费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18美元),就能够使用一个月。这种方式可以避免48%的小孩患上痢疾。赞比亚人都知道消毒剂的好处,如果问他们什么可以用来净化饮用水,98%的赞比亚人都会提到消毒剂。尽管赞比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花800克瓦查买一瓶可用一个月的消毒剂,这真的不是很贵——仅购买食用油一项,一般家庭每周都会花掉4 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1.10美元)。然而,实际使用消毒剂进行水处理的人只有10%。作为一次实验中的一部分,有些家庭会得到一张打折优惠券,可以凭券以7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16美元)买下一瓶消毒剂,而只有50%的人愿意去买。然而,当这一价格下降到3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07美元)时,愿意购买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增长。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仍有1/4的人不愿购买。
蚊帐的需求量同样很低。在肯尼亚,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TAMTAM(一起对抗疟疾),该组织在肯尼亚的产前诊所发放免费蚊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曾在同样的诊所以补贴价格(非免费)提供蚊帐,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们的组织是否有用,于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她们随机在不同的诊所提供价格不等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则采用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补贴价格。结果与消毒剂的实验十分相似,她们发现,人们对于蚊帐的价格十分敏感,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但就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约购买力平价0.75美元)来说,人们对于蚊帐的需求已经接近于零。迪帕在不同的村镇重复这一实验,但允许人们回家拿钱(而不是当场购买),更多的人以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购买了蚊帐。不过只有在蚊帐的价格接近于零时,人们的需求量才会成倍增长。
更令人困扰的是,人们虽然对蚊帐的价格很敏感,但对收入却并不敏感。要想移到S形曲线的右半部分,开启一种良性循环,即通过收入增长来改善健康状态,那么一个人因避免疟疾而增长的收入,应足以为其子女购买蚊帐,从而让他们也远离疟疾。我们还讨论过,通过购买蚊帐而降低患上疟疾的危险,可使人们年均增收15%。然而,即使收入增加15%足以买下一床蚊帐,但与其他人相比,收入增加15%的人购买蚊帐的可能性只有5%。换句话说,分发免费蚊帐远远不能保证下一代睡在蚊帐中,只能使睡在蚊帐中的人数稍有增加,即从47%增加到52%,距消除疟疾还差得很远。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
纯净水、蚊帐、抗蠕虫药片或加铁面粉,尽管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穷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证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当被问及最近一个月以来是否感到“担心、紧张或不安”时,印度乌代布尔及南非农村约1/4的穷人回答“是”。这一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而且,这种压力常常来源于人们自身或其亲属的健康(乌代布尔44%的案例)。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中,很多国家的穷人会将自己手中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在印度农村,对于那些极度贫穷的家庭来说,他们平均会将每月预算的5%花在健康上。在巴基斯坦、巴拿马及尼加拉瓜,这一比例为3%~4%。在大多数国家,超过1/4的家庭每月至少会找一次保健人员。穷人还会花很多钱来参加单一的保健活动:在乌代布尔的穷人家庭中,8%的家庭每月有记录的保健花费超过5 000卢布(购买力平价228美元),几乎是一般家庭这项预算人均月消费的10倍,而有些家庭(占1%)则会花掉26倍于月人均的预算。当碰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在乌代布尔,我们采访了三个家庭,他们目前都在还贷款,而他们当初借钱正是为了解决健康问题。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来自放债人,贷款利率非常高:每月3%(每年42%)。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为了降低保健费用,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正式的预检分诊系统,使穷人可以就近享受(常常是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最近的保健中心一般都没有医生,但那里的人员都经过训练,可以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对更严重的疾病进行检查。重症患者会被送到更高层级的医疗单位。在有些国家,这一系统由于缺乏人力,发展得较为缓慢。不过,在很多国家(如印度),医疗设施是可用的,人员配备也是充足的。即使在地域偏远、人烟稀少的乌代布尔地区,一个家庭只需步行1.5英里(约合2.4千米),就可以找到一个医疗分支机构,那里会有经过培训的护士。然而,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这个系统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穷人大多会避开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我们采访了一个极度贫困家庭的普通成年人,他每隔两个月会去一次医院,其中去公共医疗机构的次数还不到1/4,而超过一半次数去的是私人医疗机构,其余则是求助于以驱邪为主的传统治疗法。
乌代布尔的穷人似乎选择了双重昂贵的计划:治疗,而不是预防;治病找私人医生,而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医生和护士。不过,如果私人医生更有资质的话,这种选择也合情合理,但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只有约半数的私人“医生”有医学专科文凭(包括非正统学位,如印度中药医学学士和尤纳尼医学学士),还有1/3的私人医生根本没受过任何专科教育。那些所谓的“医生助手”的情况甚至更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给病人看病,但2/3的人都没有正规的医学资质。
用当地的话来讲,像这种无资质的医生被称为“孟加拉医生”,因为印度最早的一家医学院就在孟加拉邦,那里的医生从印度北部绕道而来,寻找可以让他们实践医术的地方。这一传统还在延续——这样的人还会出现在村子里,手中除了听诊器和一袋子常用药,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了。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自称是“孟加拉医生”。在我们采访时,有个人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成为医生的:“我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决定当一名医生。”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高中文凭,他曾学过地理、心理学和梵文(古印度语)。然而,“孟加拉医生”并不只出现在农村。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度德里的贫民窟,只有34%的“医生”拥有正式的医学学位。
当然,没有学位并不一定就不称职,这些医生很可能专门学过怎样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向重症患者提出到一家正规医院就医的建议。与我们交谈过的另一位“孟加拉医生”(他的确来自孟加拉邦)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会根据病情需要,拿出常用感冒药和抗疟疾药,可能还有一些抗生素。如果病情看起来很难处理,他就会建议病人去初级医疗中心(PHC)或是私人医院。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吉努·达斯和杰夫·哈默是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从印度德里市区出发,想看看医生们实际上到底了解多少。他们选择了各类医生(政府的和私人的,有资质的和没资质的),给他们每人5个与健康有关的“小场景”。例如,想象一个有痢疾症状的儿童患者,医生应对此采用的治疗方法是,先提几个问题,弄清楚这个孩子是否有发高烧或呕吐的症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可以排除那些较为严重的疾病,开一些口服补液。另一个场景是关于一位孕妇的,她带有明显的子痫前期症状,这是一种可致命的疾病,需要立即转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将医生的提问与解答方式同标准方式进行对比,列出每一位医生的称职度指数。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实验中的平均称职度指数非常低。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100名中的前20名),连一半该问的问题都没问。而最糟糕的医生(最后20名)只提出了1/6该问的问题。此外,根据专家组的评估,这些医生中大多数人给病人的建议,很可能都不会起到正面作用。那些无资质的私人医生是最糟糕的,特别是那些工作在贫穷社区的私人医生。最好的是那些有资质的私人医生,而公立医院的医生则处于中等水平。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明显失误:医生一般会诊断不足、用药过度。根据在乌代布尔的健康调查,我们发现,在一名病人去私人诊所看病的次数中,注射占66%,静脉输液占12%,而检查只占3%。治疗痢疾、发烧或呕吐的常见方法是开点儿抗生素或类固醇,或者这两样药都开点儿,而且常常采用注射的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潜在危害。首先是针头消毒的问题。我们有几位朋友曾在德里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开了一所小学校,那里有一位医生资质不明,却为很多病人看过病。在他的诊所外面,放着一个始终装满了水的大鼓,上面连着一个小水龙头。每当一位病人离开之后,这位医生就会走到外面,让大家看到他用大鼓里面的水清洗针头。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是非常小心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给某个人用过那个注射器,但乌代布尔的医生们都会谈到这位医生——他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结果使整个村子的人都染上了乙肝。
抗生素的滥用增加了抗药性细菌产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由于很多医生都习惯于替病人省钱,他们所建议的疗程比标准的疗程要短。纵观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抗生素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同样,在几个非洲国家,由于药剂量的不正确、病人的不配合,导致可以抵抗主流药物的疟原虫种出现,最终形成了一次公共健康危机。此外,类固醇的滥用所造成的潜在危害更大。在调查过印度等国穷人的研究人员当中,凡是40岁以上的都会想起这样的情景,他们曾万分惊讶地发现,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过早衰老的原因很多,但类固醇的滥用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不但会使患者的面容老化,还会使他们的寿命缩短。药物的短期效果会使病人迅速感觉良好,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穷人有时会拒绝便宜而有效的、能大大改善人们健康的方法,非要花很多钱去买那些毫无帮助的、很可能有害的东西?
因为很多有效的成果都是通过预防取得的,而这一领域的主导者长久以来都是政府,但政府总是将简单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我们看不到政府提供更多的预防保健,原因有二:政府保健服务者的高缺席率,以及动力的缺乏。
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时间也常常是关闭的。在印度,当地卫生站应一周工作6天,一天6个小时。然而,在乌代布尔,我们一年中每周都会在工作时间随机采访100多家医疗机构,结果发现,在56%的时间里,这些机构都处于关闭状态。其中只有12%是因为医护人员在附近的居民家里帮忙;在余下的时间里,根本看不到护士的踪影。在其他地方,这种护士缺席的情况也会频繁出现。2002—2003年,世界银行在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展开了一项关于缺席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保健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的平均缺席率为35%(印度为43%)。在乌代布尔,我们发现,这种缺席同样是无法预测的,穷人很难求助于这些机构。私人机构可以保证医生在岗,如果医生不在,那么他就没有收入。而政府工作人员即使不在岗,也会得到一份收入。
此外,即使政府医疗机构的医生及护士在岗,他们也不会用心医治病人。为了对同一组医生(回答场景问题的医生)进行调查,达斯和哈默研究组的一位成员跟踪每位医护人员一整天。每当一位病人来看病,研究人员都会对其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医生问了几个关于病史的问题、诊断的过程、开了什么药方,还有(私人部分)看病花了多少钱等。我们通过该研究了解到了印度医疗(公立及私人)的整体情况,结果是令人惊愕的。达斯和哈默将其称为“3–3–3”规则:平均互动只有3分钟;医生只问病人3个问题,偶尔会做一些检查;然后,病人会拿到3种药(医生常常直接开药,不写药方)。病人转诊很少见(少于全部时间的7%);只有在约一半时间里,病人才能拿到诊断说明,而只有1/3的医生会给予病人一些后续指导。然而,这似乎并不算什么,公共部门比私人机构的情况更糟。公共医务工作者诊治一个病人平均只花2分钟,问不了几个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连碰都不会碰病人一下。通常,他们只是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然后根据病人自己的判断进行治疗。几个国家的情况皆是如此。
因此,答案或许比较简单:人们尽量避免到公立医院就医,因为这个系统根本就运转不起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系统提供的其他服务(如接种疫苗和孕妇产前检查)都未得到充分利用。
不过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蚊帐并非专门由政府发放,净化水所需的消毒剂也不是。而且,即使政府医护人员真的投入工作,需要其服务的病人也不会有所增加。赛娃曼迪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与当地几家机构共同付出了约6个月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医护人员的缺席率——在岗的概率由不乐观的40%上升到了60%。然而,这并没有增加前来就诊的患者的人数。
在赛娃曼迪的另一次活动中,组织者们在相同的几个村庄按月组织村民接种疫苗。这一活动是针对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极低而发起的:在该非政府组织参与前,不到5%的儿童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规定的基本的接种服务。鉴于接种疫苗可以挽救生命(每年估计有200万~300万人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而且价格低廉(对于村民来说是免费的),这似乎应该成为每位家长的优先选择。人们普遍认为,接种率低一定是由于护士的过失而造成的。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长途跋涉到了卫生站,却找不到护士,难免心生厌烦。
2003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赛娃曼迪决定成立自己的医疗团队。通过广泛的宣传,医疗活动每月定期准时举行,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的数据证实。于是,接种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医疗团队所在的村庄,平均77%的儿童都至少接受了一次接种。不过,完成整个疗程仍是个问题。总体来说,在对照村庄里,接种率为6%;而在医疗团队的村庄里,接种率却上升至17%。然而,即使私家免费的高质量接种服务在自家门前就可以享受到,仍有4/5的儿童没有接受完整的接种。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如果人们不去公立医院,或许是因为他们对那里的服务(包括接种)并不感兴趣。为什么穷人对保健的要求如此之高,却对预防性的服务(尤其是医学为之发明的那些便宜有效的成果)置之不理?
如果人们不利用廉价的预防手段来改善他们的健康,原因是否恰恰在于这些手段是廉价的?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单纯的经济理性表明,费用一旦支付或“沉没”,将不会对使用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很多人常常表示,经济理性把这一点搞错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沉没成本”——人们更有可能会利用他们为之支付很多钱的东西。此外,人们可能会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恰恰是由于某物品是廉价的,人们便有可能认为它没有价值。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很重要。因为在健康领域,即使是研究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也一直是支持补贴的。因此,大多数廉价的成果都是低于市场价的。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一顶蚊帐不仅可以保护睡在其中的一个孩子,其他孩子也因此而不会被这个孩子传染上疟疾。一个护士治疗痢疾时用口服补液,而不是用抗生素,就能防止抗药性的传播。一个孩子因接种了疫苗而避免染上流行性腮腺炎,这也会使他/她的同学得到保护。如果这些手段更廉价,可以保证更多人对其加以使用,那么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这种补贴的手段会适得其反——使用率将变得更低,因为价格太低了。在《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威廉·伊斯特利好像已经说明了这种情况。他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比如人们将补贴的蚊帐当作婚纱。还有人提到马桶被用作花盆,甚至把避孕套当作气球。
然而,目前有大量严谨的实验表明,人们不怎么使用那些免费得到的东西的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了。有几项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回想科恩和迪帕的TAMTAM实验,结果表明,在蚊帐很廉价或免费时,人们更有可能会将其买下。这些补贴的蚊帐实际上是否会被利用?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在首次实验结束的几周之后,TAMTAM派出检查人员,对曾以各种补贴价格购买蚊帐的人进行实地家访。他们发现,60%~70%曾买过蚊帐的妇女确实都在使用。在另一次实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蚊帐的使用率上升至90%左右。此外,他们还发现,花钱买下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二者在蚊帐的使用率上没有差别。在其他一些情况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可以排除补贴降低使用率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原因不是补贴,那会是什么呢?
阿比吉特成长在一个父母来自印度两端的家庭,他的母亲来自孟买。在母亲的娘家,一种叫作“印度薄饼”的未发酵面包是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种面包是用小麦和小米做成的。阿比吉特的父亲来自孟加拉邦,那里的人们每餐都要吃很多大米饭。在怎样处理发烧的问题上,这两个地区的看法也截然不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为孟买)的每一位母亲都知道,大米可以快速地退烧。然而,在孟加拉邦,发烧时大米是禁用的:如果孟加拉邦人想说某人退烧了,那么他会说,“他今天能吃大米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曾令6岁的阿比吉特迷惑不解,于是他问自己那位来自孟加拉邦的婶婶,婶婶告诉他这与信仰有关。
更通俗地说,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组合,这显然是我们掌控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医生开的药可以治好身上的疹子,而不是应该用水蛭,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谁都没见过这样的一种随机测试,即一些肺炎患者会得到抗生素,另一些拿到的却是水蛭。的确,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测试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信念,即药物是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其他类似机构认证的。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经过某种测试,这种抗生素是不会出现在市场上的。然而,这种想法有时是错误的,因为医学测试的操作是有财务奖励的。我们信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这些研究可信度的确认,因此认为这种抗生素是安全有效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医生处方的决定是错误的,而是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大量的信念及原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当这种信任在富国出于某种原因而减弱时,我们会看到针对传统做法的激烈反应。例如,尽管权威医学小组多次确认疫苗是安全的,但美国和英国的很多人都拒绝让自己患麻疹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孩子们患上自闭症。美国的麻疹病例正在增加,不过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想一想穷国普通公民的情况。西方国家的人们可以随时洞悉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的观点,即使他们很难依此做出选择;对于几乎没什么信息来源的穷人来说,他们的选择该有多难呢?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但如果大多数人连基本的高中生理知识都不具备,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没理由去相信医生的能力与专长,因而他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的放矢。
例如,很多国家的穷人似乎都持这种理论,即将药物直接输送至血液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都愿意输液。要想驳倒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需要了解,身体是怎样通过消化道吸收营养的,针头为什么要进行高温消毒。换句话说,你至少要具备高中水平的生理知识。
更糟糕的是,了解保健知识不仅对穷人来说很难,对其他每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如果病人坚信自己需要打针才能好转,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大多数需要看医生的疾病都很难不治而愈,因此在打完一针抗生素之后,病人很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儿。这自然会使病人产生虚幻的联想:即使抗生素对治疗这种疾病没有任何效果,他们也会将病情的好转归功于它。相反,如果将结果归因于无所作为,那就不太正常了:如果一位流感患者去看医生,医生什么也没做,病人后来感觉好转,那么他就会认定,自己病情的好转与那位医生没有关系。因此,病人不会感谢那位医生,而是觉得自己这次是幸运的,如果以后又病了,一定要换一位医生为自己看病。这会导致一种倾向,即在无秩序的私人市场上寻求过度的药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开药的与看病的是同一个人,人们会找药剂师寻求医嘱,私人医生自己也会储存并销售药品。
要想通过经验了解接种或许更难,因为接种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接种了麻疹疫苗,那他就不会患上麻疹。然而,并非所有未接种的孩子都会感染麻疹(尤其是他们周围携带潜在感染原的人进行过接种)。因此,我们很难将接种与无病二者明确地联系起来。此外,接种只能预防某些疾病,还有很多其他疾病无法预防。而没受过教育的父母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接种后仍未能避免一些疾病。因此,当孩子接种后仍然得了病,家长就会觉得自己受了骗,可能决定以后都不再让孩子接种了。还有一点他们可能也不理解,为什么基本的接种体系需要很多次不同的注射——在两三次注射之后,父母们就可能会觉得已经足够了。对于健康的运转方式,人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观念。
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曾与我们交谈过的一位“孟加拉医生”向我们说明,他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化验、住院,所以他们得了点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儿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儿什么,这很重要。
实际上,较之发烧或痢疾这样的疾病,穷人为一些有可能致命的症状(如胸痛、尿血)而去看医生的概率要小得多。德里的穷人为短期病痛而花的钱与富人差不多,但富人在慢性病上会花更多的钱。不过,这可能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即胸痛有可能会发展成博帕病(一位年长一些的妇女曾向我们解释过博帕病和医生病这两种概念——她坚信,博帕病是由鬼魂引发的,因此应由传统医生来治疗)。胸痛同中风一样,大多数人都无法承担治疗费用。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肯尼亚,人们对治疗艾滋病的传统医生及传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毕竟,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其实也做不了什么(至少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变得更廉价之前),那么何不试试传统医生的草药和咒语呢?请他们来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觉到他们做了什么。由于一些症状和随机感染都是循环往复的,人们便相信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传统方式的效果。
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贫穷国家,对于那些穷国中的少数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来说,当碰到无从医治的疾病时,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在美国,抑郁和背痛是人们缺乏理解、让他们身心俱疲的两大症状。因此,美国人常常去看精神病医师、精神治疗者或瑜伽训练班及按摩师。由于这两大病症都是反复无常的,因此患者会经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每次他们都愿意相信(至少是暂时的)某种新药一定会起作用。
与真正坚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与舒适的信念或许更加灵活。我们在乌代布尔了解到,大多数去博帕的人都会去找“孟加拉医生”,还会去公立医院,他们似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信念体系的区别。他们的确会谈到博帕病和医生病,但当一种疾病很难治愈时,他们似乎不再认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而是会二者兼用。
赛娃曼迪发现,即使医疗团队每月运转良好,仍有4/5的儿童没有接受完整的接种,于是该机构便考虑该怎样提高接种率。这时,赛娃曼迪总会想到信念对于人们的意义。有些地方专家称,这一问题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信念体系。他们指出,疫苗接种在传统的信念体系中没有地位——在乌代布尔的农村及其他一些地区,传统的信念认为,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邪恶的眼睛。因此,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父母是不会把他们带到外面的。鉴于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们会说,如果不首先改变村民们的信念,要想劝服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那是极为困难的。
尽管这些观点十分有力,但当赛娃曼迪在乌代布尔建立医疗团队之后,我们仍然成功地劝说了赛娃曼迪的首席执行官尼力玛·科顿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向每次接种的人提供2磅达尔 [2] ,如果能够完成全部接种,这个人还会得到一套不锈钢餐盘。起初,赛娃曼迪负责健康计划的医生并不愿意做这个实验。一方面,贿赂人们去做该做的事似乎是不对的,他们应该学会了解什么是对健康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所建议的奖励似乎算不上什么:如果人们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接种,那么即使这样做会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也不会改变原来的想法。例如,如果他们相信带自己的孩子外出会造成伤害,那么2磅达尔(购买力平价仅1.83美元,还不到在工地干一天活儿所挣工资的一半)是劝诱不了他们的。我们和赛娃曼迪的人很早就认识了,因此我们劝服了他们,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小实验,于是他们成立了30个附带奖励的团队。结果,这些团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队所在村庄的疫苗接种率增长了7倍,上升至38%。在6英里(10千米)之内所有临近的村庄,疫苗接种率也大大地提升了。赛娃曼迪发现,赠送达尔其实反而降低了每次接种的成本,因为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带薪护士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在我们所评估的活动中,赛娃曼迪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而且可能也是挽救了最多生命的一个。因此,我们正与赛娃曼迪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致力于在其他地方重复这一实验。有意思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有些医生指出,38%的人的疫苗接种率离80%~90%的群体免疫要求还差得很远,高接种率会使整个社区的人得到全面保护。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每个国家实现90%的基本接种率,每个省市实现80%的接种率。对于医疗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来说,如果不能使一个社区得到全面保护,它就没有理由向某些家庭提供补贴,让他们做对自身有好处且应该做的事。能够实现全民接种固然很好,但这种“所有还是没有”之争只具有表面意义而已:即使我自己的孩子去接种,对于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也没什么用处,但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我的孩子,还可以保护他周围的人。因此,通过提高全面接种率来对抗一些基本疾病,即从6%提高至38%,仍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归结为一个信仰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于右派来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而对于传统的左派(包括大部分公共卫生群体及赛娃曼迪的良医)来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奖品,还是得到奖品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贬低。相反,我们应专注于劝服穷人,让他们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
我们认为,在思考接种及其他类似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原因有两个:第一,实验表明,至少在乌代布尔,穷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但他们的很多信念并不坚定。他们不会因害怕邪恶的眼睛而拒绝接受达尔,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无法对疫苗的费用与好处进行评估。当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举一个令人遗憾但很重要的例子,比如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他们并不容易贿赂。因此,尽管穷人的某些信念很坚定,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认为,行动都带有目的性:如果人们相信接种的价值,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接种。这并非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其中的含义十分深远。
疫苗接种遇到的阻力并不是很大,这表现在,在没有达尔奖励团队的村庄,77%的儿童都首次接受了疫苗接种:即使没有任何奖励,人们一开始似乎也愿意进入接种流程。问题在于,怎样使他们完成整个流程。这也正是全部接种率未超过38%的原因——奖励机制使人们来接种的次数增多,但不足以使他们完成全部5次接种,而那份免费的不锈钢餐盘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原因:年复一年,我们都很难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年新愿望(比如定期去健身馆),尽管我们知道健身会使我们远离心脏病。心理学研究目前已可解释一系列的经济现象,表明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时间矛盾”概念)。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欲望支配:花一点点时间(排队等着给自己的孩子接种)或放弃一点点舒适感(肌肉需要被唤醒)都是我们当前需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迫切感的情况下去想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顿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因吃得太饱而放弃马上运动的想法),当前的这种感觉更令人不愉快。当然,我们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奖品”(糖果、香烟等);但当我们为将来而计划时,那种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倾向于推迟小额度的花费。那么,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们花的,而是由明天的我们花的。关于这一概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当明天成为今天,相同的逻辑便会重现。同样,我们可能会推迟购买一床蚊帐或一瓶消毒剂,因为我们的钱当前有更好的用途(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卖诱人的海螺馅饼)。这个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点点花费使人们对采用挽救生命的方法犹豫不决,为什么小小的奖励可以鼓励人们使用这种方法。2磅达尔之所以有用,因为这是母亲今天就可以拿到的东西,可以抵消她为孩子接种疫苗所付出的代价(花了几个小时带孩子抵达医疗团队所在地,接种有时会引发低烧)。
如果这种解释没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基本原理,用于规范一些具体的预防性保健行为,或是提供超越传统争论的一些经济奖励,使我们的社会有理由补偿或加强那些有利于他人的行为。罚款或奖励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这是他们心中向往却总是在拖延的行动。更通俗地讲,时间矛盾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要使人们尽可能轻松地去做“正确的事”,或许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选择。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二人,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该大学的法律学者,在二人所著的畅销书《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 [3] 中,他们推荐了大量这方面的参考办法。其中一种重要的概念就是“默认选项”:政府(或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应将他们认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选择定位为默认选项,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就会积极地朝这个目标行动。当然,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但要为此而花一点儿钱。结果,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选择默认选项。小小的奖励(如接种疫苗而赠送的达尔)也是点拨人们的另一种方式,这给了他们一个今天就行动的理由,避免了他们无限期的拖延。
关键的挑战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助推物品”。例如,用消毒剂净化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你需要时刻记着这件事:首先需要购买消毒剂,然后在任何人饮水之前,将适量的消毒剂滴入水中。由此可见自来水的巨大好处——家里可直接饮用经过消毒的水,用不着我们去想这件事。那么,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们怎样提醒人们为自家的饮用水消毒呢?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想到了一个办法:提供一种叫作“转一圈”的免费释氯器,安装在村庄的水井旁边,每个人都会在这里取水,释氯器的把手每转一圈都会释放适量的氯元素。这使氯化水的过程变得极为容易,很多人每次取水时都会往水中添加消毒剂。因此,在所有随机对照实验证实的干预手段中,这是预防痢疾的一种最廉价的方式。
不过,有一次我们并没这么幸运。当时我们与赛娃曼迪设计了一个加铁面粉的计划,用以应对蔓延的贫血症。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我们设置了一个内在的“默认选项”:一个家庭需要一次决定其是否参与。此后,参与家庭所使用的面粉将永远是加铁面粉。然而,遗憾的是,磨坊主(无论他们为多少面粉加铁,都只收取统一的费用)所提供的奖品是以相反的“默认选项”为前提的:除非家庭提出要求,否则不给面粉加铁。我们发现,这点小小的加铁费用,足以使大多数人灰心丧气。
助推还是说服?
在很多情况下,“时间矛盾”会阻碍我们将目的转化为行动。然而,在接种的具体例子中,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人们不了解接种的好处,那么“时间矛盾”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无限期地延迟决定。对于那些一味拖延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欺骗自己。他们不仅要决定下个月去医疗团队,还要确保自己下个月一定会去。我们有些天真且过于自信地以为,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做正确的事。然而,如果父母们真的相信接种的好处,他们似乎不会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欺骗自己,假装自己真的会在下个月付诸行动,等到整整两年过去才发现为时已晚。我们稍后会提到,穷人可以找到强迫自己省钱的方法,这需要具备十分灵活的经济头脑。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接种疫苗就像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那样完美,他们可能就会想出方法,克服自身拖延的天性。更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拖延接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接种的好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些家庭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应采纳一些建议,这时助推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预防性保健就成为这种政策的最佳候选:好处只能在未来兑现,而且无论如何都很难了解这些好处到底是什么。幸运的是,助推可能有助于说服,并由此启动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还记得赠送给贫穷肯尼亚家庭的蚊帐吗?我们曾就此事争论过,第一床蚊帐使得到蚊帐的孩子多挣到一些钱,但这些钱不够他再给自己的子女买蚊帐:即使蚊帐可以使一个孩子的收入增长15%,但这只会将他们再买蚊帐的概率提高5%。然而,收入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家庭可能会注意到,在使用了蚊帐之后,孩子生病的次数少了。此外,他们可能还会了解到,蚊帐使用起来很简单,睡在蚊帐中也并非像他们起初想的那样不舒服。帕斯卡利娜·迪帕在一次实验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验证:找到那些曾以很便宜的价格或免费得到蚊帐的家庭,还有那些曾以全价买下蚊帐的家庭,再次向他们出售蚊帐,结果大多数人都没买。迪帕发现,较之曾以全价买下第一床蚊帐的家庭,曾免费或在大减价时获得蚊帐的家庭,更有可能会再买一床蚊帐(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一床蚊帐)。此外,迪帕还发现,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更有可能会为自己买一床蚊帐。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即使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全无恙,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谁也没有那么明智、耐心或博学到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样,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而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规范病人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鉴于人们对价格的高度敏感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免费提供预防性服务,或是奖励那些利用这种服务的家庭,使其尽量成为自然的“默认选择”。免费的释氯器应放在水源旁边;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应得到奖励;学校里的孩子们应得到免费的抗蠕虫药片和营养增补剂;至少在人口密集地区,水利及卫生设施的公共投资应立即启动。
作为公共卫生投资,通过减少疾病与死亡、提高人们的收入,很多这类补贴的价值都超出了其自身的成本——不再反复患病的孩子可以上更长时间的学,因而可以在成年后挣更多的钱。不过,我们并不可以就此认为,这一切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即使在预防性措施十分廉价的情况下,如果关于其好处的信息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当前的习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投入多少钱都会受到限制。而如果那些措施不那么廉价的话,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自然是钱。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一挑战是双重的:既要确定人们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药品,还要限制他们获取不需要的药品,从而防止药物依赖性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由谁来开展实践并充当医生的角色,这似乎是大多数政府都难以规范的。因此,要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及强效药的滥用,唯一的方法或许就是,尽最大努力控制这类药品的销售。
这一切听上去都颇具家长式风气,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对于生活在安全而干净的家中、躺在舒适沙发上的我们来说,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告诉自己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是轻而易举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目前不正是这种家长式作风的永久受益者吗?我们深深扎根于这一体系而浑然不觉。这个体系不仅可以将我们照顾得更好,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思考生活中的其他问题。然而,我们仍然有责任向人们传授公共卫生知识。我们确实欠每个人(包括穷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解释,告诉他们为什么接种疫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完成整个接种疗程。不过,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仅凭信息并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对于穷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一样。
[1] 口服补液,也称ORS,是一种混合盐、糖、氯化钾及兑水抗酸剂的儿童口服剂。
[2] 达尔,即干豆。当地的一种主食。——编者注
[3] 本书中文简体版于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009年夏天,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那甘纳吉村,我们见到了40岁的寡妇珊塔玛,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珊塔玛的丈夫4年前死于急性阑尾炎,她没有保险,家里也拿不到任何抚恤金。三个年长一点儿的孩子都上了学,至少上到了八年级,但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14岁女孩)都辍学了,女孩在邻居家地里干活儿。我们认为,由于父亲的去世,孩子们被迫辍学,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便开始干活儿挣钱。
然而,珊塔玛纠正了我们的想法。丈夫去世后,她便将家里的地租了出去,自己开始干临时工,挣的钱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需求。珊塔玛的确让女儿去田里干活儿,但那是在她辍学之后,因为珊塔玛不想让她待在家里没事儿干。其余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在三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中,有两个在我们见面时还是学生(最大的女儿22岁,已经结婚了,很快就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了解到,她的大儿子在最近的城镇雅吉尔上大学,将来准备成为一名老师。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之所以辍学,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去上学。村庄附近有几所学校,包括一所公立学校和几所私立学校。那两个孩子原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他们经常逃学,最终母亲放弃了让他们上学的打算。在我们采访期间,那个10岁男孩一直和他的母亲在一起,嘟囔着上学没意思。
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上不起学。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上小学是如此。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学可上。然而,我们在全球所开展的各种调查显示,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辍学往往并不是由于家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有时可能是健康原因所引起的,比如在肯尼亚,孩子们会因接受抗蛔虫治疗而耽误几天课。尽管如此,辍学情况或许还能反映出孩子们并不想上学(这可能很普遍,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这种状态),而且他们的父母似乎也无力或不愿让他们去上学。
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全面提升教育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如果没有强大的潜在教育需求,那么建立学校、聘用教师又有什么用呢?相反,如果人们对技术有真正的需求,那么对于教育的需求自然就会显现,供应便会随之而来。然而,这一乐观看法似乎与珊塔玛孩子的故事不相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是印度的IT中心班加罗尔,它对人才的需求量自然很大。珊塔玛一家中有一位未来的教师,他们意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因此愿意进行教育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学生不具有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需求,也不是因为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呢?
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样,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争的主题。正如援助一样,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每个人或许都会同意,受教育总比不受教育要好),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而且,尽管教育与援助所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但二者内部的分界线实际上处于同一位置,提供援助的乐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是教育干涉主义者,而提供援助的悲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支持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
长久以来,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至少是国际政策领域)一直认为,教育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将孩子们带进教室,最好由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师任教,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这类人强调“供应学校教育”,我们将他们称为“供应达人”。这里借用的是印度的一个俗语——“供应商”(西印度语中的这类绰号有拉克达瓦拉——木材供应商、达路瓦拉——酒品供应商、邦度瓦拉——枪支贩卖者等),以便与供应经济学派区分开来。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或许,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供应达人立场的最清晰的表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于2000年取得共识的8个目标,预计在2015年之前实现。其中第二、第三个目标分别是,“确保到2015年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以及“到2005年,争取消除初中等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并在2015年之前消除各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在印度,目前95%的儿童可以在距家不到半英里的学校上学。几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加纳)已开始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大批孩子进入学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在1999—2006年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学入学率由54%上升至70%,在东亚及南亚则由75%上升至88%。全球学龄儿童的辍学人数由1999年的1.03亿减少到了2006年的7 300万。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即使是那些极为贫穷的人(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其子女入学率目前也在80%以上(被调查国家中至少有9个国家是这样)。
虽然普及中等教育(9年级以上)并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但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5—2008年之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学入学率由25%上升至34%,南非由44%上升至51%,东亚则由64%上升至74%。不过,中学的学费也变高了:聘用教师需要更多的钱,因为这些教师必须是更有资质的;而且对于父母及其子女来说,他们放弃的收入及劳动市场经验有更大价值,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干活儿挣钱了。
让孩子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正是学习的起点。然而,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有些奇怪的是,学习的问题并未被摆在国际声明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2000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全民教育峰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在峰会的会后公报中,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被排在了第六名,即第六个目标。这其中的隐含意义或许是,学到什么没有入学重要。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2002—2003年,由世界银行发起的世界缺席调查秘密派出一些调查员,到6个国家的公立学校进行抽样调查。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的教师平均每5天就会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乌干达的教师缺席率是最高的。此外,印度的调查显示,即使教师在校并授课,他们也经常在喝茶、读报或是和同事聊天。总体来说,印度公立学校50%的教师都在上课时间缺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学习呢?
布拉翰(Pratham)是印度一家专门致力于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于2005年决定进行深入研究,查明孩子们究竟在学些什么。布拉翰成立于1994年,其创立者为化学工程师马达夫·查万。查万拥有美国教育背景,他在创立布拉翰时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所有儿童都应该学会阅读,并通过阅读来进一步学习。该组织成立之初,查万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将这家位于孟买的小小的慈善机构,发展成了印度最大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或许也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布拉翰的计划涉及约3 450万印度儿童,而且目前正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在《年度国家教育报告》(ASER )的指导下,布拉翰在印度的600个地区建立了志愿者小组。这些小组在每个地区都随机选择了几个村庄,对每个村庄的1 000多名儿童进行了测试——参加测试儿童总数为70万——并总结出了一份成绩单。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看到了这份报告,但他从中所读到的却令他心情沉重。7~14岁年龄组中接近35%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段落(一年级水平),而几乎60%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二年级水平)。只有30%的孩子会做二年级的数学题(基本除法)。这些数字令人十分震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在自家的摊位或商店里帮忙,总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做一些更复杂的计算。难道学校让孩子们变得不会学习了?
并非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阿卢瓦利亚先生一样豁达。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拒绝相信政府的表现如《年度国家教育报告》所暗示的那样糟糕,于是便组织自己的团队再次展开测试。很遗憾,测试结果只是印证了原有的数据。1月,在印度的一次年度活动上,ASER 的测试结果被公之于众。报刊对可怜的测试分数表示沮丧,学者们在专题小组会上讨论着那些数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印度并非个案,其邻国巴基斯坦、遥远的肯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肯尼亚,效仿ASER 的尤维佐调查发现,27%的5年级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英文段落,23%的孩子读不懂斯瓦希里语(小学的两种教学语言),还有30%的孩子不会做基本除法。在巴基斯坦,80%的三年级孩子读不懂一年级的课文。
一些批评家(包括威廉·伊斯特利)认为,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供教育。对于需求达人来说,这一结论涵盖了几十年来所有教育政策的缺点。在他们看来,教育质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就在于家长们对教育不够重视,他们觉得教育真正的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回报”)并不多。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根本无须政府的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私立学校,如果私立学校学费太贵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当地政府建立学校。
需求的作用确实很重要。入学率与教育回报率息息相关:在印度的“绿色革命”期间,成为一名成功的农夫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学习的价值也有所上升。在一些更适合播种“绿色革命”所引进的新种子的地区,其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近期,离岸呼叫中心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欧洲及美国,人们常常指责这种呼叫中心减少了当地的工作机会,但它却大大增加了印度年轻女性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印度一次小规模社会革命的一部分。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延森与一些这样的呼叫中心合作,随机选择了印度北部3个城邦很少有人去招聘的几个村庄,在那里组织针对年轻女性的招聘会。结果在意料之中,较之其他一些未实施这种招聘方式的随机选择的村庄,这些村庄业务流程外包中心(BPOs)的年轻女性的就业率得到了提升。更为显著的是,这部分地区原本可能是印度歧视女性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招聘工作启动三年之后,招聘点所在村庄中5~11岁女孩入学的概率提高了5%。这些孩子的体重也有所增加,这表明家长们将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他们发现,让女孩受教育同样会带来经济价值,因此乐于投资。
在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应方面,家长们有能力应对变化。因此,对于需求达人来说,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没有教育政策。只要找到一些急需人才的行业,让投资于这些行业变得富有吸引力,那么就会出现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方面的供应压力。这样,争论便会继续下去,因为家长们开始真正关心教育,他们会向教师施压,让教师根据他们的需要授课。如果公立学校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私立学校市场便会趁势形成。有人称,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会让家长们得到适合他们孩子的高品质教学。
需求达人观点的核心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将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家长,而未来获得收益的是他们的孩子。而且,尽管实际上很多孩子会为他们的父母带来投资“回报”——给他们养老,但很多孩子并不愿那样做,甚至“不履行义务”,将他们的父母遗弃。即使有的孩子很孝顺,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因多上了一年学而多挣的那一点点钱,能够转化成父母们的收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心生悔恨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非常富有,可以在外面自立门户,却让他们晚景悲凉。保罗·舒尔茨是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自己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时说,父母曾经反对他上学,因为他们想让西奥多留在农场。
的确,孩子学习成绩好,家长也会为之自豪(他们喜欢与邻居分享这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家长从孩子那里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或许也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因此,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家长都有权支配他们的孩子——由家长来决定谁去上学,谁留在家里或是出去工作,以及他们的收入如何支配。有些并不重视教育的家长很在意孩子长大后会回报给他们多少钱,这样的家长或许会在孩子10岁时就让他辍学,并安排他出去工作。换句话说,教育的经济回报(其衡量尺度为受教育孩子的额外收入)固然很重要,但其他很多因素或许也不容忽视,比如我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对自己的孩子是否宽容。
“没错,”供应达人说道,“这就是有些家长需要点化的原因。儿童有权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及充分的教育,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允许这一权利被父母的冲动或贪婪所剥夺。”要降低送孩子上学的费用,建立学校、聘用教师是必要的一步,但这或许还远远不够。这一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强制规定:当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必须送他们上学,除非父母能证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教育孩子。然而,这在国力较为有限、义务教育难以强化的情况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从经济角度考虑,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这就是教育政策所选择的新工具背后所折射出的理念:有条件现金转移。
圣地亚哥·莱维是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4—2000年期间任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主要任务就是改革错综复杂的福利体系,其中包括几个截然不同的计划。莱维认为,如果将福利金与人力资本投入(健康与教育)相结合,培养身心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人,那么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的角度来看,今天花掉的钱都将有助于消除贫穷。这一想法激发了一种新的名为“进步”的教育计划的产生,这是一个“有附带条件的”转让计划,也是第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CCT)计划:贫穷家庭会得到某些救助,但前提是他们的孩子定期上学,而且这个家庭得采取预防性保健措施。如果孩子上了中学,或者女孩也上了学,那么家长就会得到更多的钱。为了使该计划合法化,这笔钱被当作一种“补偿”支付给一些家庭,补偿他们因让孩子上学而非工作所损失的工资。然而,实际上,无论家长怎样看待教育,只要让他们觉得如果不送孩子上学就会受损失,该计划就会达到点化他们的目的。
圣地亚哥·莱维还有另一个目标——确保该计划不会因政府的换届而受影响,因为每届总统常常会取消其前任的所有计划,并制订自己的新计划。莱维认为,如果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府就不会轻易取消它。因此,莱维首先制订了一个试点计划,只面向随机选择的一组村民,这样便可以清晰地比较他们与其他村民的情况。该实验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一计划的确大大提升了入学率,尤其是中学的入学率。女孩的中学入学率由67%上升到了约75%,男孩则由73%上升到了约77%。
这展现出了一次成功的随机对照实验的说服力,但这也仅仅是这类实验的首批成果之一。政府换届时,这一计划也幸存了下来,只不过更名为“机会项目”。然而,莱维或许没有预料到,他带来了两个新的传统。第一,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漫布整个拉丁美洲,随后又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区。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也采用了这一计划。第二,当其他国家启动自己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时,他们常常会开展一组随机对照实验,用来评估这项计划。在某些测试中,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怎样更好地实施该计划。
矛盾的是,在马拉维,正是这些实际应用案例使我们得以反思这一教育计划的成功。它的制约性体现在,光增加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家长也需要得到一种激励。研究人员及从业者们由此发问,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是否能取得与有条件现金转移相同的效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极具煽动性,它表明,制约性似乎根本不重要——研究人员向有学龄女孩的家庭提供5~2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现金。在一组对象中,现金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孩子要入学;在第二组对象中,现金转移没有任何条件;第三组对象(对照组)则没有现金转移。这一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一年之后,对照组孩子的辍学率为11%;而其他两组孩子的辍学率只有6%),有条件现金转移与无条件现金转移的效果是相同的。这表明,家长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学,他们只是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已。
有几个因素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现金转移在马拉维产生了一定作用:或许是家长们付不起学费,或许是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孩子可以挣到的钱。当然,借钱供自己10岁的孩子上学,并指望他在20岁时能挣到钱,这简直就是一个白日梦。现金转移可以使家长们摆脱极度贫困的状态,或许也拓宽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让他们拥有更长远的人生观:教育必须现在投入,而这部分费用要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得到补偿。
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收入与教育息息相关:贾马尔将受到的教育不如约翰多,因为他的父母更贫穷,即使两人受教育的回报一样多也是如此。的确,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随着调查的深入(从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到每天生活费为6~10美元的人),教育费用在生活费用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增加。如果每个有收入家庭的儿童人数随收入而大幅度减少,那么每个孩子的教育花费比总花费增长得更快。这与教育只是一种投资的情况恰恰相反,除非我们愿意相信,穷人没有受教育的能力。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父母的收入对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很关键,那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即使无任何天赋,也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穷人家的孩子则有可能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因此,让市场操纵一切,并不能让每个孩子(无论他来自哪类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除非我们能够完全消除收入差距,否则公共供应方的干预就是必要的,这种干预可以使教育变得更廉价,使我们更容易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次机会。
然而,问题在于,尽管从原则上看完美无缺,但这种公共干预是否切实可行呢?如果家长们根本不关心教育,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推动只会浪费资源,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例如,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称,非洲国家的教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毫无助益。
同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研究特定国家在实施这种政策时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教育质量低下,但学校还是有用的。在印度尼西亚1973年第一个石油繁荣时期之后,时任该国总统的苏哈托将军决定大规模修建学校。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刺激供应计划:学校的建立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则,即优先考虑失学儿童人数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些地区没有学校,就说明人们对教育不感兴趣,那么这个计划就是一次可悲的失败。
实际上,总统特别基金计划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为了评估该计划,伊斯特利找到了一些成年人(可以受益于新建学校的年轻人)和更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的年龄已使他们错失到这些学校上学的机会),并对二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伊斯特利发现,相对于年长的一代,在建立了更多学校的地区,年轻人的收入要高得多。通过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伊斯特利总结出,因新学校的建立而每多接受一年小学教育的人,其收入将提高约8%。这一针对教育回报的估算,与美国的普遍情况十分类似。
另一个自上而下的经典计划就是义务教育。1968年,台湾地区做出了一项规定,要求每个孩子必须接受9年的教育(之前的规定为6年)。对于孩子们的学校教育以及他们的就业前景,这项规定都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对女孩来说尤为如此。教育的好处不仅在于金钱——在中国的台湾地区,这一计划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也很大。在马拉维,那些因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而没有辍学的女孩,其怀孕的概率也有所降低。在肯尼亚也是如此。目前,一个对此方面颇有研究的重要团体正致力于验证教育的深远影响。
此外,这一研究还总结出,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使人受益匪浅。那些喜欢阅读的人会轻松阅读报纸和公告栏,从而得知他们何时会从一项政府计划中受益。接受中级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即使没有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们也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这两种在哲学层面上相互对立的策略似乎再次失去了重点,供应策略与需求策略没有理由互相排斥。供应本身就会带来好处,但需求也很重要。的确,当城里出现了合适的工作机会,有的人虽未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但也找到了受教育的途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来自他们居住区域所建学校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教育策略一定会带来很多好处。我们看到,学生们的确在公立学校里学到了东西,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基于需求的方法是否会更有效?私立学校就是由需求推动的标准策略——即使有免费的公立学校,家长们仍会花费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将他们的孩子送入一所私立学校。难道说私立学校破解了教育质量的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在完善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应发挥重要的作用。近期通过的印度《教育权利法案》得到了政界(包括“左”派,全世界的“左”派一直都反对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凭证私有化的一个体现——政府给予公民“凭证”,用来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
在教育专家提出警告之前,全球很多雄心勃勃的低收入家长已经决定,即使省吃俭用,也必须将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一个惊人的现象由此产生,整个南亚及拉丁美洲出现了很多廉价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每月的学费仅为1.5美元。而且,它们一般都很低调,常常是以某人家里的几个房间作为教室,老师通常都是一些当地人,因找不到其他工作而决定办学校。一项研究表明,在巴基斯坦的一个村庄里,能够准确反映私立学校供应情况的是,该地区以前是否建过一所女子中学。有些受过教育的女孩会寻找本村的挣钱机会,她们中有很多人都在村里当教师,进入教育领域。
尽管这些女孩的资质令人怀疑,但私立学校常常比公立学校效率更高。世界旷工调查发现,在印度,在公立学校教师出勤率较低的村庄,私立学校存在的概率更大。此外,与同一村庄的公立学校教师相比,私立学校教师于指定日在校的概率平均高出8个百分点。上私立学校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会很好。ASER 称,2008年,印度47%的公立学校五年级学生达不到二年级的阅读水平,而私立学校同等水平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32%。在巴基斯坦学校学习及教学成就(LEAPS)调查中,与公立学校的孩子相比,私立学校的孩子在上三年级时,英语水平就已超前1.5年,数学水平超前2.5年。的确,那些决定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的家庭或许是出于经济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私立学校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也很有吸引力:私立学校学生与公立学校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近乎10倍于最富阶层孩子与最穷阶层孩子之间的平均差距。在同一家庭里,即使这一差距没有那么大(这一点或许有些高估了教育的回报,因为父母可能会将最有天赋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或是以其他方式帮助这个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与上私立学校的孩子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因此,私立学校的孩子比公立学校的孩子学到的更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完美无缺。在比较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经过简单干预后的教学质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私立学校的缺陷。
布拉翰是一家著名的非营利教育机构,该机构负责ASER 的运营。该中心不仅揭露了教育系统的缺陷,而且还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与该机构合作,几乎参与了其儿童教学及阅读教学的每一项新计划的评估。2000年,在印度西部城市孟买及巴罗达,ASER 正式开始运营。在那里,布拉翰实行了其所谓的“儿童之友”计划。该计划从每个班里选出20个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将他们送到“儿童之友”——由团队中的一位年轻女性负责,研究他们各自具体的弱点。尽管经历了一场地震及地区动乱,该计划对这些孩子测试的结果仍取得了很大的收益——在巴罗达,私立学校所获的平均收益幅度几乎是印度的两倍。然而,与普通私立(或公立)学校的教师相比,这些“儿童之友”所受过的教育要少得多——他们很多人只上过10年学,外加在布拉翰受过一周的培训。
鉴于这些结果,很多组织都宁愿固守已有的成就,但布拉翰却并非如此。原地踏步绝不是布拉翰创立者查万的性格。精力充沛的鲁克米尼·班纳吉也是一样,他一直推动着布拉翰的迅速发展。布拉翰对更多儿童进行研究的一种途径就是,找一些组织接管该计划。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一个邦,也是最穷的邦之一。在北方邦东部的江布尔区,布拉翰的志愿者们走遍一个又一个村庄,对那里的儿童进行测试,并鼓励整个机构都参与进来,看看孩子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在孩子犯错误时,家长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打自己的孩子——但后来,机构里出现了一组志愿者,他们时刻准备着帮助这些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志愿者们大多为年轻的大学生,傍晚,他们在附近的居民区里开课。布拉翰为这些志愿者们提供一周的培训,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补偿。
我们也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评估,结果令人十分惊讶:在计划结束时,所有参与该计划的孩子都已经认识字母了,而他们在计划实施之前还不会阅读(相反,在年底之前,对照村庄认识字母的孩子仅有40%)。那些最初仅能读懂字母的孩子,在参加了该计划之后,能读懂短篇故事的概率比没参加计划时提高了26%。
近期,布拉翰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了与公立学校体系的合作之上。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的一个邦,也是教师旷工率最高的一个邦。布拉翰为中小学生组织了一场救助性的夏令营,邀请一些公立学校教师前来授课。这一评估结果令人十分震惊:这些备受批评的公立学校教师其实教课了,而且收益也可与江布尔夜课所获得的收益相媲美。
布拉翰的实验结果使得印度乃至全球的很多学校都正在与这个组织联系。目前,加纳正在对该计划的一个版本进行测试,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是一个研究小组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他对那些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到学校里提供救助性教育服务。塞内加尔及马里的教育部代表团参观了布拉翰的活动,并考虑在本国复制这一计划。
这不禁让人觉得,如果那些志愿及半志愿教师可以创造这么大的成效,那么私立学校显然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还应做得更好。然而,我们得知,在印度的私立学校,有1/3的五年级学生还达不到一年级的阅读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很高,为什么我们在公立学校体系中看不到这一点呢?如果孩子们很容易取得较高的学习成就,为什么家长们没有需求呢?为什么在布拉翰的江布尔计划中,只有13%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参加夜校呢?
毫无疑问,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许,私立学校之间缺乏一定的竞争压力,或者家长们没有获取足够的指导信息。稍后,我们将探讨几个更广泛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等。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公立学校的教师表现得这么差。不过,教育所特有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于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几年前,在乌代布尔农村地区,我们在由赛娃曼迪管理的一个民间学校组织了一次亲子拼贴画活动。我们提供了一堆五颜六色的杂志,让家长们从中剪出一些图片,以表现他们对于教育的想法,以及教育能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什么。这一活动的构想是,让家长们在自己孩子的协助下完成一张拼贴画。
结果,家长们完成的拼贴画看上去都大同小异:拼贴画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黄金及钻石首饰,还有各种时下流行的名车模型。实际上,杂志中还有其他可用的图片——宁静的乡村景象、渔船、椰子树等。然而,如果他们的拼贴画中所表现的元素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些元素一定不是教育的全部。家长们似乎总将教育看成一种让自己孩子获取大量财富的方式。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期望中的致富途径就是一份政府工作(如教师),其次是某种办公室工作。在马达加斯加,640所学校的学生家长们曾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孩子们上完小学之后应怎样谋生、上完中学之后又该怎样谋生。70%的家长认为,一名中学毕业生会得到一份政府工作,而实际上只有33%的中学生得到了这种工作。
然而,能够上到六年级的孩子为数并不多,更别说通过毕业考试了。目前,这种水平是任何要求教育背景的工作的最低资质。而且,家长们并非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在马达加斯加,当家长们回答对于教育回报的看法时,他们一般都能做出正确回答。但是,他们对于教育优势和劣势的回答却有些极端——他们将教育看成一种彩票,而不是一种安全的投资。
帕克·苏达诺是印尼万隆西卡达斯贫民窟一个收废品的人,他实事求是且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他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最穷的人”。当我们2008年6月见到他时,他的小儿子(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就要上中学了。苏达诺认为,小儿子上完中学之后,很可能在附近的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在那儿上班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小儿子早就应该得到了——但不管怎样,苏达诺认为让他上完中学是值得的,即使这让他少拿了3年的工资。苏达诺的妻子认为,这个孩子或许还能上大学,而苏达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白日梦——他认为,小儿子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份办公室工作,从安全及体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对于苏达诺来说,碰碰运气是值得的。
家长们会认为,前几年的教育付出比以后的教育付出少得多。例如,马达加斯加的家长们认为,每一年的小学教育会使一个孩子增收6%,每一年的初中教育增收12%,而每一年的高中教育则会增收20%。我们在摩洛哥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家长们认为,每一年小学教育可以使一个男孩增收5%,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则增收15%。而女孩在这种情况中的差别则会更明显。在家长们看来,每一年的小学教育对女孩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仅为其增收0.4%,但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则可以为其增收17%。
据估计,每一年的教育实际上都会按比例或多或少地增加收入。而且即使对于未得到正式部门工作的人来说,教育似乎也是有好处的。例如,相对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来说,受过教育的农民在“绿色革命”期间挣的钱要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非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家长们看到的是一条实际不存在的S形曲线。
这条S形曲线表明,除非家长们愿意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否则他们只能孤注一掷,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认为最有前途的那个孩子身上,确保这个孩子接受足够的教育,而不是将教育投资分摊给所有的孩子。在珊塔玛(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家附近,即那甘纳吉村里,我们见到了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农户家庭。家里除了最小的那个12岁男孩,其他孩子上学都没超过两年。他们对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因此这个12岁孩子只在那里上了一年学,然后就转学到村里的一家私立寄宿学校上7年级。孩子一年的学费会超过这个家庭农作物总收入的10%,这项投入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很大了,显然,他们供不起7个孩子全部上学。这个幸运男孩的母亲向我们解释道,他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用“笨”或“聪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当着孩子们的面,那情形就像选出一位世界冠军(并让家里其他人都支持这位冠军)似的。这种想法会催生一种特殊形式的同胞竞争。布基纳法索的一项研究发现,智力测验得分高的孩子,更有可能被学校录取,但当他们的兄弟姐妹得分高时,他们入学的概率就会降低。
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一项关于有条件现金转移的研究发现了将所有资源花费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合理性依据。该研究的资金有限,家长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适龄孩子参加抽签,中签的孩子只要按时上学,其家长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现金转移。中签者越按时上学,就越有可能在下一个学年继续学业。在该研究的另一个版本中,现金转移的条件是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中签者更有可能会上大学。令人不安的一个发现是,有些家庭让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参加抽签,其中只有一个孩子中签了,那么与孩子都未中签的家庭相比,这些中签孩子的兄弟姐妹上学的概率会有所降低。家庭收入的增加固然不会对此造成影响,却会让中签的孩子从中受益。一个冠军产生了,所有的资源便集中到了他(或她)的身上。
误解也是个关键问题。实际上,教育应该不存在“贫穷陷阱”: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但家长们认为教育的回报呈“S”形,这在无意识中营造着一个“贫穷陷阱”,进而催生一个真正的“贫穷陷阱”。
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都包含着这种思想。学校的课程及结构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那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出当地的精英,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与当地人的不同等级。尽管新生大量涌现,教师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顺利进入下几个学年或大学学习。与此相关的一种残酷压力是使课程“现代化”,更具有科学性,并且变成更厚更沉的课本——因此,印度政府目前将一二年级学生书包的总重限制在6.6磅(2.72千克)。
有一次,我们跟随布拉翰的成员来到印度西部巴罗达的一所学校,学校事先得到了通知,一位教师显然想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在黑板上写出一串十分复杂的数字,巧妙地列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随后对图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解。所有孩子(三年级学生)都整齐地坐在地板上,表现得很安静。有的孩子可能想在自己的小石板上写数字,但粉笔的质量太差了,根本写不出来。显然,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位老师也不例外。我们见过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即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具有精英偏见。在与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合作中,伊斯特利对肯尼亚的一个班级进行了重新安排,利用多余的一个教师将学生们分成两组。这一区分使孩子们学到了以前没学过的知识。于是,教师们通过抽签被随机安排到“高级”或“低级”学区。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教师常常很沮丧,他们在授课中什么也得不到,还会因自己的学生成绩差而备受指责。因此,他们也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在随机访问中发现,与被安排到“高级”学区的教师相比,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教师教课的概率更低,他们更有可能会在办公室里喝茶。
问题并不在于学生们没有雄心壮志,而是家长们对于学生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期望不高。我们曾前往喜马拉雅山印度段的山区,对犹他拉坎德孩子们进行测试。那是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不免让人觉得测试是一件烦人的事——参加测试的孩子肯定是这么想的。当我们问他是否上学时,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还会问他一些问题时,他似乎也很配合。但当测试者递给他一张表格时,他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一个7岁孩子常常会这样做。测试者尝试着让他看一眼表格,许诺给他几张漂亮的图片,再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的母亲一直嘟囔着鼓励的话,不过她的努力显然缺乏热情,这表明她不希望孩子改变主意。在测试结束之后,当我们走向车子时,一位腰间系着满是灰尘的短腰布(当地农民系的一种缠腰带),身穿一件黄色T恤衫的长者与我们同行,他说“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让我们去猜他的后半截话。我们在一位母亲的脸上见过同样的忧郁,很多母亲的脸上都有这种表情。她们想说,我们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在谈及关于穷人的话题时,我们常常会提到某种过时的社会决定论,例如,与阶级和种族相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晚期,吉恩·德勒兹带领一个小组,就印度的教育状况撰写了一份报告,即印度的《基础教育公开报告》(Public Report on Basic Education Revisited ),其中一个发现就是:
很多教师非常不愿意到偏远或“落后”的村庄去,一个现实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或是偏远村庄的生活设施太差……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他们不熟悉当地村民,据说那些村民常常把钱都用来喝酒,这些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潜质,或是“行为举止就像野蛮人一样”。偏远及落后地区常常被看作是教师的耕耘得不到收获的地方。
一位年轻的教师甚至告诉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与“粗俗父母的孩子”进行交流。
为了证实这种偏见是否会影响教师对待学生的行为,教师们在一项研究中被要求为一组考试评分。他们并不认识那些学生,但随机选出的半数教师都被告知一个孩子的全名(包括种姓),其余都是匿名的。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相对于教师们看不到学生所处阶层的情况,他们在得知学生所处阶层时给予底层学生的分数更低。然而,有意思的是,这样做的并非是来自上层的教师。来自底层的教师实际上更可能给予底层学生更低的分数,他们一定认为这些学生是拿不到好成绩的。
过高的期望加上信心的缺失,会造成十分危险的结果。我们看到,相信S形曲线使人们选择放弃。如果教师和家长不相信孩子能够跨过顶峰,进入S形曲线的陡峭部分,那么孩子自己或许也不会尝试:教师会忽视成绩落后的孩子,家长也不再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然而,这种行为会产生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贫穷陷阱”。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许能取得好成绩。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取得好成绩的家庭,或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家庭,他们最终会证实自己“较高”的期望。阿布比特小时候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较差,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学得比全班同学都快,因而感到厌烦了。于是,阿比吉特被转到了二年级,但很快他的学习成绩又落后了。老师甚至把他的作业本藏了起来,怕成绩好的学生看到后会质疑他是怎么跳级的。如果阿比吉特的父母不是学者而是工人,那么他肯定早就被送去接受救助性教育或是勒令退学了。
孩子们在评估自己的能力时,也会运用这种逻辑。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展示了他所谓的美国“刻板印象威胁”的力量:那些未被告知数学能力差的女士,在数学测试中的成绩会更好;非裔美国人如果一开始就必须在试卷上填写自己的种族,那么他们的测试成绩则会更差。继斯蒂尔的研究之后,来自印度北方邦的两位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自己的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竞赛猜谜。他们发现,只要阶层不被突显出来,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做得一样好,而一旦低阶层孩子得到提醒,意识到他们正在与高阶层孩子竞争(方法很简单,即在比赛之前问他们的全名),他们的表现就会差一些。作者称,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担心比赛组织者的评判会有失公平,但也可能是这种“刻板印象威胁”的一种内化体现。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块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就像珊塔玛的孩子一样拒绝去上学。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额外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功能,但这种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克雷默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寻找一个简单的测试案例,旨在对该国的政策干预进行一次初度随机评估。在第一次尝试中,他想找到一个没有争议的案例,这样,干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课本似乎是完美的选择:肯尼亚西部的学校(开展这项研究的地方)几乎没有课本,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课本是最重要的投资。研究人员从100所学校中随机挑选了25所,并将课本(官方指定的课本)发放到这些学校中。令人失望的是,收到课本的学生与没收到课本的学生,二者的平均测试分数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克雷默及其同事发现,在收到课本的学校里,一开始成绩很好的孩子(研究开始之前测试分数接近最高分的学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问题的本质显现了。肯尼亚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本也自然是英文课本。然而,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英语只是他们的第三语言(排在当地方言及肯尼亚斯瓦希里语之后),他们的英语说得很差。因此,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英文课本的用处并不大。在很多地方,各种形式的此类实验相继展开(从发放活动挂图到提高教师比例)。但是,在教学方法或鼓励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投入收效甚微。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私立学校在普通学生教育方面表现一般——他们的重点在于,为某种艰难的公共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孩子,因为那是通往更大成功的踏脚石。这种考试需要有超前的学习能力以及全面的教学大纲。然而,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都跟不上,这一现实虽然令人遗憾,却是不可避免的。阿比吉特在加尔各答所上的学校实行一种较为开放的政策,即每年开除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因此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该班便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通过率。肯尼亚的小学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至少从六年级起是这样的。因为家长们也支持这种政策,他们没理由向学校施压,去改变这种行为。家长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希望学校向孩子们提供他们心目中的那种“精英式”教育——不过,他们根本无法实际检验这种教育,更不去想他们的孩子能否真正从中受益。例如,英语教学特别受南亚父母们的欢迎,但对于不会说英语的家长们来说,他们无法得知教师是否在用英语教学。同样,家长们对夏令营和夜校也几乎不感兴趣——对于那些没有“中签”的孩子们来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布拉翰的暑期补习班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公立学校教师似乎懂得怎样去教成绩较差的孩子,他们甚至愿意在暑假期间为此投入努力,但在常规的学年期间,这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近期,同样是在比哈尔邦,我们对布拉翰的一项鼓励计划进行了评估。培训教师利用他们的材料,培训志愿者做教师助理,从而将救助性教育计划全面应用到公立学校中。在那些教师与志愿者都接受了培训的(随机选择的)学校中,效果非常明显,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布拉翰实验结果一样成功。然而,在只有教师接受了培训的学校里,结果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些在夏令营中表现较好的教师们,在此次计划中却表现平平:官方的教学方法以及过于注重教学大纲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似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对此,我们不应将全部责任都推到教师身上。根据印度新的《教育权利法案》,完成规定课程是法律中所要求的。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这种思想及行为体系意味着,大多数学校体系都有失公平,还很浪费资源。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仅可以去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从而使他们的潜力得到真正的挖掘。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一开始就会表明,除非这些孩子表现出某种超凡的天赋,否则他们就会被开除,而实际上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或许大多数)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从爱因斯坦到印度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他们二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都非常有名气。而拉曼公司的故事则表明,这种经历或许并非只限于少数的优秀人士。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拉曼的泰米尔工程师在迈索尔创立了拉曼公司。该公司制造工业用纸制品,例如电力变压器所用的纸板等。一天,拉曼在工厂门口发现了一个名叫兰加瓦米的年轻人,他是来求职的。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来自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有一定的工程教育背景,但他只有一张资格证书,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学学位。由于他坚持说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强,拉曼对他进行了一次快速智力测验。测试结果令拉曼印象深刻,于是他决定将这个年轻人留下来,以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一开始他还需要拉曼的指导,后来逐渐开始独立完成任务,并能想出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拉曼的公司最终由瑞典的跨国公司巨头ABB(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目前是ABB全球(包括在瑞典的)众多分公司中效率最高的。兰加瓦米虽然没有工程学位,却成为工程领域的带头人。他的同事克里斯那查理也是被拉曼发现的——他以前是个木匠,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而他目前是该公司一个主要部门的经理。
阿伦是拉曼的儿子,他在公司被收购前曾接管公司一段时间,目前他与在拉曼公司时的几个手下共同经营着一个小型研发公司。他的核心研究小组共有4人,其中有两人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其他两人也不具备工程师的资质。阿伦说,他们都非常聪明,但刚开始时,他们没有信心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呢?正因为公司的规模较小,需要完成很多研发工作,他们才被发现。即便如此,要发掘他们的能力,还需要通过大量耐心的工作及不断的鼓励。
这一模式显然并不容易复制。问题是,人才的发掘不存在捷径,除非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教育体系应该做的事情——给予人们足够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长处。然而,拉曼公司并非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有很多人才仍未被发现的公司。印孚瑟斯公司是印度的IT巨头之一,已建立了自己的测试中心,应聘者(包括那些没有正式资质的人)可以走进中心,接受一次智力及分析能力(而不是课本)测试。测试成绩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实习生,优秀的实习生便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对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这一可选方案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印孚瑟斯公司关闭了其测试中心,这在当时的印度是头版新闻。
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变得越来越艰难。纵观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入学率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而随着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全球对于有教学经验者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现在,这些人都去当程序员、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及银行家了。因此,找到中级以上的优秀教师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太难办了?
一个千真万确的好消息是,我们现有的一切证据都有力地表明,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学好基本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实现,但前提是人们能够专注于此。
以色列一个著名的社会实验表明,很多学校都能够做到这一点。1991年,15 000名贫穷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及其子女,在一天之内离开了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疏散到以色列各地。这些犹太孩子的父母们平均都上过一两年学,他们的孩子与其他以色列孩子一起上小学。还有一组家庭的孩子既有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也有刚从那里移民而来的,他们的父母平均上过11.5年学。两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别极大。几年之后,当1991年入学的孩子即将中学毕业时,两组人的差别缩小了很多。一直上到了十二年级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占总数的65%,而从俄罗斯移民而来的孩子的这一比例稍高,为74%。结果显示,即使是家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条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至少在符合条件的以色列学校中是这样的。
一些成功的实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如何创造这种条件的启发。第一个因素就是,关注基本技能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每个孩子及其老师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就能掌握这些技能。这不仅是布拉翰计划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态度,与美国特许学校“不要找借口”的意味类似。这些学校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IPP)”计划学校、哈莱姆儿童地带等,主要面向贫穷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其课程侧重于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以及不断测量孩子的认知水平,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就不可能对孩子们的进步进行评估。
通过对奖励入学赢家与输家的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学校的办学效率很高。对波士顿特许学校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将特许学校的规模扩大4倍,同时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不变,可将全市黑人与白人孩子在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缩减40%。这种机制正是我们在布拉翰计划中看到的:在一般学校体系中迷失的孩子(在进入特许学校之后,他们的考试分数落后于其他孩子)又得到了一次机会,很多人都抓住了这次机会。
还有一项关于布拉翰计划的研究表明,培养一位合格的救助性教师相对容易,至少就低年级教学来说是这样的。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能够成为这类老师的志愿者一般都是大学生,或是经过10天教学培训的人。此外,他们的教学内容并不仅限于阅读及基础数学的教学。比哈尔邦的这一计划安排志愿者们走进教室,教那些在学习时能充分发挥自己阅读能力的孩子,布拉翰将其称为“阅读式学习”,也就是更基础的“学会阅读”的续篇,其效果十分显著。特许学校主要聘用充满活力的年轻老师,他们对中小学孩子的学习帮助很大。
而且,通过对课程及学生进行分组,让孩子们以适合自己的进度学习,确保落后的学生专注于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实现巨大的收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目的也在于此。在肯尼亚,前面提到的一项研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两组,并对两种不同的实验模式进行比较。在第一种模式中,孩子们被随机分到一个教室里,而在另一种模式中,他们则被以知识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组。此时,教师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要,每一知识水平的孩子都会取得进步。而且,这种效果是持久的:到三年级期末时,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时被追踪的学生,其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于未被追踪的学生。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将年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具灵活性。如果一个孩子根据年龄应该上五年级,但他需要完成二年级的某些课程,那么他就可以先上二年级而不会觉得难为情。
一般来说,要改变一个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马达加斯加的一项计划告诉家长们,让家庭背景与他们相似的孩子多上一年学,其家庭的平均收入就会提升,孩子的成绩也会受到很大的积极影响。有些家长发现自己低估了教育的好处,教育为其带来的收益可达到原来的两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早期研究中,高中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由于教师向家长传递信息是完全免费的,目前在所有经过评估的干预方法中,这是已知的提高考试分数的最廉价的方式。
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对于教师及学生来说都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太过专注于难以定性的多年以后的成果。肯尼亚的一项计划提供购买力平价20美元的年度奖学金,获得者是在一次考试中得分排名前15%的女孩。该计划不仅使女孩们更努力地学习,还促使教师更努力地工作(帮助女孩)。这意味着,男孩们即使没有奖学金,也会更努力地学习。在美国,对实现长期目标(如得高分)的孩子给予奖励并没有效果,但对他们增加阅读量给予奖励却被证实非常有效。
在当今世界,好老师很难找到,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使用成本也越来越低,因此,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教育部门对于在教学中使用技术的观点并不十分积极。但这种经验主要是基于富裕国家的,它们的计算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另一个选择,即找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活力的教师取而代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在贫穷国家并不容易做到。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效果虽然不明显,但仍透出了其积极的一面。2000年年初,在印度巴罗达的一所公立学校,我们与布拉翰联手对该校的一项计算机辅助学习计划进行了评估。这项计划很简单,几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按要求在计算机上玩游戏。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逐渐难算的数学题,如果学生成功地算出每道题,他们就有机会射击外太空的垃圾(这一游戏很有挑战性)。尽管学生们一周只能玩两个小时的游戏,但这一计划对于提高其数学成绩起了不小的作用,效果相当于多年来各领域尝试过的最成功的教学干预法。总的来看,事实确实如此——最优秀的孩子做得更好了,成绩最差的孩子也取得了进步。这明显展现出了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好处:每个孩子都能根据这一计划调整自身的学习节奏。
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与某些教育专家的观点是相悖的。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理解——我们似乎是在建议一种双重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是为富人的孩子设置的,他们无疑会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接受最高标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余下的孩子设置的。对此的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但遗憾的是,这种差别已经存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目前的体系似乎根本没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如果课程得到彻底的简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有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不过,要想与那些上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他们的确还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他们学会相信自己,他们就可能抓住一次机会,当这一体系愿意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时尤为如此。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桑 贾伊·甘地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也是她的法定继承人。不幸的是,桑贾伊1981年死于一场坠机事故。他认为,人口控制是印度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所谓的非常时期(1975年年中—1977年年初),人口控制成为桑贾伊多次公开露面所探讨的一个主题。在这一时期,民主政权瓦解,桑贾伊虽然没有任何官职,却公开地活跃于政治领域。“‘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得到‘最高的重视’,”他在一次简短的讲话中说道,“如果人口继续以现有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业、经济及农业发展都将毫无意义。”
印度的计划生育具有悠久的历史,该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71年,喀拉拉邦推出流动节育服务,这种“节育阵营”法成为桑贾伊·甘地制订非常时期计划的基石。尽管在他之前的大多数政客都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桑贾伊·甘地无论是在热情度上,还是能力(及意愿)上,都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行他所选择的政策扫清了很多障碍。1976年4月,印度内阁通过了一项正式的国家人口政策声明,要求采取大量措施鼓励计划生育,其中非常显著的一个措施就是,对于同意做节育的人给予丰厚的经济奖励,如多付一个月的工资或优先进入福利分房名单。更可怕的是,政府居然授权每个城邦制定强制节育法(对象为子女超过两个的人)。尽管只有一个城邦提议制定这项法律(但未通过),但各个城邦都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外界压力,纷纷列出节育名额并努力加以实现。除了三个城邦之外,其他所有城邦都“自愿”选择了比中央政府设定的更高的目标,即在1976—1977年之间,力争实现860万次节育。
一旦提出来,这一目标便不能被忽视。北方邦政府给其主要手下发电报称,“通知每个人,如果不能实现月度目标,他们不仅会被停发工资,还会被停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立即通知整个机构,继续通过无线电每日向我及部长秘书报告执行进度”。直至乡村级别的每位政府职员(包括铁路稽查员及学校教师)都要了解当地的目标。教师会对学生家长进行走访,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做节育,他们的孩子以后就有可能不被学校录取。有些人乘火车不买票——这是当时穷人的普遍做法——除非他们选择节育,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毋庸置疑,这种压力有时还会蔓延至其他领域。尤他瓦是首都德里附近的一个穆斯林村落,一天晚上,该村所有男村民都被警察召集到一起,警察假装送他们到警察局接受罚款,实际上是送他们去做节育。
这一政策似乎已经实现了其短期目标,不过这种激励政策可能会导致实际节育数量的误报。1976—1977年间,报告称825万人做了节育,而其中650万人都显示是在1976年7~12月做的。到1976年年底,21%的印度夫妇都做了节育。不过,该计划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激起了广泛的民愤。1977年,印度最终举行了选举,辩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节育政策的讨论,其口号最具纪念意义——Indira hatao,indiri bachao(大意是“节制性欲,远离印度”)。人们普遍认为,英迪拉·甘地之所以会在1977年的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计划使其失了民心。因此,新政府立即推翻了这一政策。
这一举措包含着一种历史学家所喜欢的讽刺意义,即从长远角度来看,桑贾伊·甘地反而促进了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非常时期的大肆宣扬,计划生育政策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并且长期存在——有些城邦(如拉贾斯坦邦)仍然本着自愿的原则推广节育政策,但除了当地的卫生机构,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然而,对于国家动机的普遍怀疑,似乎也成了非常时期最顽固的“残留物”。例如,人们仍然常常听说,贫民窟及村里的人拒绝注射小儿麻痹症滴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给孩子做节育的一种秘密手段。
这一特别情况及中国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都是加强人口控制措施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其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人口政策。1994年《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的约翰·邦加茨预计,到1990年,第三世界85%的人口所生活的国家中,其政府都会明确表示人口过多,需要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予以控制。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担心人口增长问题,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多原因。杰弗里·萨克斯在其《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 )一书中谈到了这些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增长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人口增长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导致全球变暖。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饮用水逐渐减少,部分原因也在于人口的增长。同时,人口增长还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加大,因此需要更多的水用于灌溉(70%的淡水可用于灌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淡水稀缺的地区。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但那些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家庭却并不把这当回事,或许这就是政府出台某种人口政策的原因。问题在于,要想制定一种合理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生那么多孩子: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生育吗(如采取避孕措施),还是他们不想节育?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例如,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总生育率 [1] 为每个妇女生6.12个孩子,其贫穷程度是美国的51倍,而美国的总生育率仅为2.05。
这种有力的联系使很多人(包括那些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相信,托马斯·马尔萨斯18世纪所提出的那个古老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国家拥有多少资源基本上是固定的(他擅长以土地为例),因此人口增长一定会使国家变得更穷。根据这一逻辑,黑死病在1348—1377年间导致了英国一半人口的死亡就成就了随后的高薪时期。近期,也就是艾滋病泛滥非洲的时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扬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在一篇题为《死者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Dying )的文章中称,非洲未来的几代人将受益于因这种传染病而导致的生育率降低。这一生育率的降低既有直接原因,即人们不愿进行未受保护的性生活,也有间接原因,即劳动力的减少使更多女性选择工作,而不是生孩子。扬估算,在未来几十年,南非人口的减少足以抵消很多艾滋孤儿缺乏适当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由于艾滋病毒的直接影响,南非的富裕程度将增加5.6%。他通过观察进行了总结,这无疑是为了他那些过分挑剔的读者,“人们不能无休止地哀叹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的灾难,又总结说人口不增长同样是一场经济灾难”。
扬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艾滋病毒是否真的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细致的后续研究否定了这一观点。然而,人们大多愿意接受扬的另一观点——降低生育率可以使每个人变得更富有。
不过,这一观点并非如听上去那么明确。毕竟,与马尔萨斯最初提出其论题时相比,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增长了很多倍,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比马尔萨斯时代的人更富有。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技术进步这一因素,但它确实帮助人们发掘了很多潜在资源。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寻求新的想法,因而技术突破或许更容易实现。的确,在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更多的地区或国家往往发展得比其他地区快。
因此,仅靠理论不太可能解决问题。当今生育率较高的国家更穷这个事实并不完全因为生育率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育率高恰恰是由贫穷引起的,或是有第三个原因导致了高生育率及贫穷。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常常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如20世纪60年代的朝鲜和巴西),即使这一“事实”并不是绝对的。难道很多家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就开始少生孩子,还是由于他们没时间照顾那么多孩子?或者生育率的降低让他们节省了一部分资源用于其他投资?
同样,如果想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转换视角,先将大问题放在一边,专注于穷人的生活与选择。首先,我们看看家庭内部的情况:大家庭更穷的原因是其人口太多?他们对于子女教育及健康的投资能力较低?
桑贾伊·甘地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一个小家庭才是一个快乐的家庭”。通常,这句口号后面还附上了一张卡通图片,上面画着一对笑呵呵的夫妇带着两个胖嘟嘟的小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印度,这是极为常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对此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论断。贝克称,每个家庭都面临着一种所谓的“质与量的取舍”,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更多的孩子,每个孩子的“质”就会降低,因为父母为每个孩子投入的食物及教育资源就会更少。当父母相信(无论是对是错)为最有“天赋”的那个孩子投入更多是值得的时候,情况尤为如此。我们已经谈到,这正是S形曲线所反映的情况。这样一来,很多孩子最终会失去决定其命运的机会。如果生在大家庭的孩子接受适当的教育、营养及医疗的概率较小(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贫穷家庭更有可能成为大家庭(比如说他们无力承担节育费用),这就产生了一种跨代传递贫穷的机制,即贫穷父母会生育更多的贫穷子女。这种“贫穷陷阱”或许能为某种人口政策提供根据,即杰弗里·萨克斯在《共同财富》一书中提出的论点。但这是真的吗?生长在较大家庭的孩子具有明显的劣势?在我们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生于大家庭的孩子一般接受的教育较少,但不一定各地都一样——印尼农村、科特迪瓦及加纳就是例外。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即由于一些孩子的兄弟姐妹很多,所以他们注定要贫穷,并且受的教育较少。原因也可能是,有些贫穷家庭不仅孩子较多,对教育也并不十分重视。
要想验证贝克的理论并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家庭人口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孩子人力资本投入的减少,研究人员尝试研究一些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人口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在这些案例中,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在较小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鉴于全球大多数穷人不使用增育的方法,家庭之所以会意外地生下更多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了双胞胎。例如,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两个孩子,但产妇在第二次生产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样第一个孩子就比预期多了一个弟弟或妹妹。性别构成是另一个原因。很多家庭常常想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就意味着,与已经有了一双儿女的家庭相比,如果一对夫妇两次生育的孩子属于同一性别,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她有了一个妹妹,那么与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相比,前者更可能会有两个或更多弟弟妹妹,因为在子女性别选择技术发明之前,生男生女是没法预测的。以色列一项专门调查家庭大小变化原因的研究表明,大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并无不利影响,即使对于以色列的阿拉伯穷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不免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南希·钱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她发现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结果:在某些地区,这一政策较为宽松,允许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再生一胎。南希发现,由于实行了这一政策,那些多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女孩与独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显然有违贝克的理论。
另一项证据来自孟加拉国的蒙塔拉伯。这一地区实施了一项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计划,内容与自愿计划生育有关。1977年,141个实验村中有一半村子被选中接受一项集中计划生育服务计划,即计划生育及母婴保健计划(FPMCH)。每隔两周,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会前往已婚育龄妇女的家中,提供计划生育上门服务,但前提是这些妇女愿意接待她。此外,护士还会提供产前保健及疫苗接种服务。这一计划大大减少了出生人口数,或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到1996年,与未实行这一计划的地区相比,实施这一计划的地区30~55岁的妇女平均少生了1.2个孩子。这一计划还导致婴儿死亡率减少了1/4。由于该计划的直接干预,儿童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因此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便与生育率无太大的关联了。不过,尽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儿童健康的投资加大,到1996年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身高、体重、入学率或上学年限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同样,质–量关系似乎没能发挥作用。
当然,这三项研究或许并不能成为定论,我们还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但就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关证据的解读不同于萨克斯《共同财富》中的论点,即尚无有力证据表明,更大的家庭对孩子不利。就这点而论,我们很难证实,全套的计划生育措施可以避免儿童生长在大家庭。
然而,大家庭对孩子无不利影响,这似乎也有些违背常理:如果同样的资源要由更多人来分享,最终有些人就会得到更少。如果孩子没受委屈,究竟是谁吃亏了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母亲。
哥伦比亚的Profamilia生育计划项目表明,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担心。该项目由年轻的产科医生费尔南多·塔马约于1965年创立,是几十年来哥伦比亚的主要避孕措施提供单位,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计划生育项目之一。到1986年,53%的哥伦比亚育龄妇女使用的避孕工具,主要是通过Profamilia获得的。在青春期就通过该计划了解计划生育的女性,其上学的时间更长,而且在正式部门工作的概率更大。
与此类似,受益于蒙塔拉伯计划的孟加拉妇女在身高和体重上均优于对照组,她们赚的钱也更多。避孕措施使妇女对自身育期有了更大控制权——她们所能决定的不仅是可以生几个孩子,还有什么时候生。而且,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过早怀孕对于母体健康非常不利。此外,过早怀孕或结婚常常会导致辍学。然而,将计划生育定位为保护母亲的社会愿望衍生了很多问题:如果妇女不介意在错误的时间怀孕,这一切又怎么会发生呢?更为普遍的是,家庭怎样做出节育的决定?妇女在这类决定上有多大控制权?
穷人或许无力控制自己的生育,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接触不到一些现代的避孕措施。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官方报告,通过满足现代避孕“未满足的需求”,能将每年的意外怀孕次数从7 500万次减少至2 200万次,每年可减少27%的产妇死亡率。与更加富有及受过教育的妇女相比,贫穷及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概率更小。此外,近10年来,贫穷妇女对于现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并没有提高。
然而,使用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获取渠道。在计划生育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活跃于教育领域的那种供需之战。而且,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供应达人与需求达人常常是同一组人。供应达人(如杰弗里·萨克斯)强调获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人生育率要低得多;需求达人反驳说,这一关联只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确的避孕法,无须外界的帮助,因而仅仅拓宽获取避孕措施的渠道并无多大用处。
为了确认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唐娜·吉本斯、马克·皮特及马克·罗森茨魏希不辞辛苦,找出了印尼几千个地区在1976、1980及1986年的计划生育诊所数量,并将这方面的数据与乡村级生育调查数据进行对比。结果他们发现,诊所较多的地区生育率较低。然而,他们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的降低与诊所数量的增加并无关联。他们进而认为,计划生育设施会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提供,但这些设施对于生育率的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1分;供应达人得0分。
蒙塔拉伯计划一直是供应达人的代表作。他们声称,提供避孕措施可以发挥作用,至少这是一个仍须讨论的证据。我们看到,1996年,实验区的30~55岁妇女比对照区妇女平均少生1.2个孩子。但蒙塔拉伯计划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避孕措施,其中一个主要环节就是,一位女性保健工作者每隔两周为足不出户的妇女提供上门服务,打破了对某些地区避孕问题讨论的禁忌。(因此,这一计划的花销很大——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估计,与典型的亚洲计划生育项目相比,蒙塔拉伯计划为每位育龄妇女每年提供的花费要比原来花费多出35倍。)因此,该计划直接改变了理想的家庭子女数量,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某些可以控制生育的工具,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自1991年起,该计划实施区域的生育率不再下降,与未实施计划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缩小。1998年,也就是我们记录数据的最后一年,计划实施地区的生育率为3.0%,对照区为3.6%,而孟加拉国其他地区则为3.3%。蒙塔拉伯计划或许只是增强了节育的趋势,该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因此,双方在这一局最多也就打了个平手。
关于哥伦比亚Profamilia计划的研究也认为,该计划对于总生育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Profamilia计划使妇女一生仅仅少生约0.05个孩子,低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生育率降低的10%。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2分;供应达人得0分。
因此,这一数据似乎公平地将胜利送到需求达人的手中:避孕渠道或许可以向人们提供比现有选择更方便的节育方式,让他们感到满意,但这似乎并不能降低生育率。
然而,扩大避孕渠道的好处在于,帮助青少年推迟怀孕期。Profamilia计划在哥伦比亚做到了这一点,它帮助妇女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遗憾的是,在很多国家,青少年被禁止获取计划生育服务,除非他们的父母提供正式许可。青少年的避孕需求最有可能得不到满足,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不承认青少年性行为的合法性,或者认为青少年控制能力不强,不能正确使用避孕措施。结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拉丁美洲,青少年的怀孕率极高。世界卫生组织称,科特迪瓦、刚果及赞比亚的青少年怀孕率超过10%,而在墨西哥、巴拿马、玻利维亚及危地马拉,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在8.2%~9.2%之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名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为4.5%)。此外,在这一问题及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的问题上,我们所付出的那点努力似乎并没切中要害。
埃斯特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证明了这种错失良机的后果。在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协助下,她对一些女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女学生的年龄在12~14岁之间,没怀过孕。通过对她们进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调查,她们的平均怀孕率分别为5%、14%及30%。青少年怀孕不仅本身令人不快,还标志着危险的性行为。在肯尼亚,这意味着怀孕者更容易染上艾滋病毒。肯尼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官方策略,也是民众团体、各类教堂及国际组织与政府协商的一种微妙权衡的行为,即强调禁欲是唯一安全的解决办法。其策略为:禁欲(Abstain)、忠贞(Befaithful)、使用避孕套(Condom)……否则你就会死去(Die)(简称“ABCD”策略)。在学校,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避免婚前性行为,对于避孕套则不会加以讨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鼓励这一做法,并将预防艾滋病的经费专门用于禁欲计划。
这一策略认为,青少年的责任心不强、不够理性,无法权衡性行为及使用避孕套的代价及好处。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不接触性(或至少避免婚前性行为)则是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然而,埃斯特、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在肯尼亚开展的几个同期实验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选择性行为对象及性行为条件上,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在第一项研究中,为了对“ABCD”策略进行评估,研究人员随机选择了170所学校,安排教师接受关于“ABCD”课程教学的培训。结果并未出乎意料,这一培训增加了学校关于艾滋病教育的时间,但所报告的关于艾滋病性行为及认识并没有变化。此外,通过在干预实施后对他们进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跟踪调查,无论是在教师接受了培训的学校中,还是在教师未接受培训的学校中,青少年的怀孕率都是相同的,这表明,危险性行为的范围并没发生任何变化。
在相同学校开展的另外两个策略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第二个策略只告诉女孩们一些她们不知道的知识,即较年长的男人比较年轻的男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15~19岁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同龄男性的5倍。这似乎是由于年轻女性与感染率较高的年长男性发生性行为而引起的。“甜爹”计划只是告诉学生们,哪一类人群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其目的是减少女性与年长男人(即“甜爹”)的性行为,但有意思的是,该计划还旨在促进女性与同龄男性受保护的性行为。一年之后,在未接受该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5.5%;在接受了该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3.7%。这一比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性伙伴为年长男性的女性的怀孕率降低了67%。
第三个计划只是通过提供校服,让女孩们更容易待在学校里。一年之后,在提供校服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从14%降至11%。更明确一点儿说,那些因免费校服而待在学校里的女孩们,每三人中就有两人推迟了其初次怀孕的时间。令人好奇的是,只有在那些教师未接受新式性教育课程的学校里,才集中体现了这一效果。在那些提供艾滋病教育及校服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与未实行任何计划学校中的女孩并没什么差别。艾滋病毒教学课程并没有减少青少年的性行为,反而抵消了校服的积极作用。
将这些不同的结果整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图景便显现了出来。肯尼亚的女孩大都知道,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会导致怀孕。但如果她们认为,一旦为有钱的“甜爹”生下一个孩子,那么他一定会负责任地照顾自己,因此怀孕或许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实际上,对于买不起校服而不能留校的女孩来说,相对于那种未婚辍学女孩的一般结局——只是待在家里成为全家的负担,成家、生孩子或许是一个较有吸引力的选择。而较为年长的男性往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伴侣(至少在女孩不知道他们更有可能携带艾滋病毒的情况下),因为年轻一点儿的男性还没能力成家。女孩们因校服而留在学校里,并因此而避免了怀孕,从而降低了生育率。但由于性教育计划鼓励结婚而不鼓励婚前性行为,因此这一计划只对那些为自己找丈夫(在一定程度上是位“甜爹”)的女孩有效,并会抵消校服的作用。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很大程度上,穷人(即使是少女)对于自身生育、性欲及节欲方式(或许是些不太好的方式)的选择都极为谨慎。如果明知怀孕对于自己来说代价很大,却仍然这样选择,那么这就说明她们是主动的。
然而,当我们思考生育这一选择时,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生育是谁的选择?生育决定是由一对夫妇做出的,但女性最终将付出生孩子的大部分身体代价。毫无疑问,她们对于生育的选择与男人迥然不同。在一些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调查中,男性和女性需分别回答一些问题。与自己的妻子相比,这些男性常常表示大家庭更理想,并且始终对避孕措施的要求较低,因此女人在家里有多大决定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一个女人比她的丈夫年龄小很多,接受的教育也少很多(这都是早婚所造成的后果),她会发现自己很难和丈夫对抗。这种情况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也取决于她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她是否有离婚的自由及离婚后的生存选择。当然,这种可能性还取决于她与丈夫所处的受公共政策影响的法律、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例如,在秘鲁,如果妻子拥有财产权的话,她所在的家庭就会拒绝生育(相对于那些女人没有财产权的家庭),不过财产权要写在妻子与丈夫的共同名下才可以。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女人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她就会在家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因而在决定家庭成员数量上拥有更大的权威性。
夫妻之间的矛盾也表明,尽管避孕本身对于降低生育或许没多大作用,但避孕方法上的小小变化却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纳瓦·阿什拉夫和埃里克·菲尔德向赞比亚首都卢萨卡836位未婚女性提供了一种凭证,使她们可以与一位计划生育护士私人预约,免费享受一系列现代避孕措施。有些女性是自己来领凭证的,有些则是当着自己丈夫的面领取的。阿什拉夫和菲尔德发现,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很大:与当着丈夫的面领证的妇女相比,单独领证的女性拜访计划生育护士的概率高出23%,要求获得一种隐蔽避孕形式(注射避孕法或避孕品植入)的概率高出38%,在9~14个月后意外分娩的概率降低了57%。蒙塔拉伯计划比其他计划生育活动更频繁地改变生育选择,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通过对妇女进行家访(假定她们的丈夫不在家),女性保健工作者可以让她们在丈夫不知情时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相反,对于那些受限于足不出户的传统(一个女人被禁止单独出门)的女性来说,她们需要丈夫陪同自己去市中心接受服务,这种情况或许会使她们改变主意。
蒙塔拉伯计划效果显著(特别是在早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该计划会加快社会变革。生育转型需要一定时间,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这个问题有发言权的不是夫妻,而是大众。生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及宗教准则,违反这一准则就会受到惩罚(被排斥、嘲笑或宗教制裁)。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社区如何定义这一行为。在实施蒙塔拉伯计划的地区,这种变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社区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的女性,这不仅体现了一种新的准则,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改变准则的信息。
凯文·孟希对蒙塔拉伯计划中社会准则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他谈到,一位年轻女性这样描述自己与同龄人之间的讨论:“我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哪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最合适……我们是否应采取计划生育措施……我们过去常常从用过(避孕方法)的人那里寻求答案,如果一对夫妇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这一消息就会迅速传播开来。”
孟希发现,在实施蒙塔拉伯计划的村庄,都会有一位社区保健工作人员。在过去6个月里,如果同一宗教信仰的村民使用避孕措施的频率较高,那么女性自身采取避孕措施的概率也会更大。虽然村里的印度教徒及穆斯林都能接触到同一位保健人员,而且获取避孕措施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但当穆斯林看到其他穆斯林采取避孕措施时,他们便会照做,印度教徒也是如此。而印度教徒采用避孕措施却对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毫无影响,反之亦然。孟希认为,这一模式无疑意味着,女性会在社区内逐渐了解可接受的行为是怎样的。
在传统社会中,讨论社会准则的变换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要提出某些问题并不容易(避孕会违反宗教教义吗?会不会让某人永久丧失生育能力?应到哪里获取避孕措施?),因为提问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人的倾向。结果,人们常常从最不安全的渠道获取信息。在巴西这个天主教国家,计划生育并不为国家所提倡。然而,电视剧非常受欢迎,特别是环球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肥皂剧。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收看环球频道的范围迅速扩大,肥皂剧的收视率也有所上升。20世纪80年代,肥皂剧进入热播时期,而剧中的人物无论是从阶级还是社会态度上看,都与普通巴西人相异:尽管普通巴西女性在1970年差不多都有6个孩子,但肥皂剧中大多数50岁以下的女性都没有孩子,其余的也只有一个孩子。一旦肥皂剧在一个地区出现之后,那里的新生儿人数便会急剧下降;此外,该地区有孩子的女性会根据肥皂剧中的主角,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肥皂剧呈现了一种迥异于巴西人所习惯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并产生了一些独具历史意义的结果。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在巴西刻板的社会中,对于很多有创新及进步思想的艺术家来说,肥皂剧最终成为他们的选择出路。
关于“穷人能控制其家庭决定吗?”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从最明显的层面来看,他们能控制——他们的生育决定是一种选择的产物,而且即使缺少避孕措施,似乎也不会构成一个太大的障碍。同时,他们无法立即控制的某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女性或许会受到不得不生更多孩子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或社会准则。于是,一个不同于桑贾伊·甘地所采用的政策,也不同于当今善意的国际组织所制定的政策的结论产生了:增加避孕措施获取渠道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尽管有了巴西电视台的案例,但改变社会准则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准则或许也是社会经济利益的体现。难道穷人要生很多孩子仅仅因为这是一种不错的经济投资?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经济未来:一种保障政策、一款存储产品,也是某种福利彩票,这些东西被统统装进了一个大方便袋。
帕克·苏达诺是印尼西卡达斯贫民窟的一个收废品的人,他有9个孩子和一大堆孙子孙女。苏达诺将自己最小的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他认为这是一次值得一投的赌注。我们问他,有这么多孩子他是否快乐,他回答说“当然”。他解释道,他的9个孩子中有几个混得不错,可以给他养老送终。不过,孩子越多,他们出问题的危险也就越高。实际上,帕克·苏达诺的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三年前就失踪了。苏达诺为此感到很难过,但至少还有8个孩子让他感到欣慰。
富裕国家的很多父母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因为他们有其他安度晚年的方式——他们有社会保险、共有基金及退休计划,还有公共或个人医疗保险。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会详细地讨论,为什么像帕克·苏达诺这样的人无法享受这些服务。现在,我们评论的仅仅是,对于全球大多数穷人来说,子女(还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给父母养老的观念是极为平常的事。例如,2008年时,中国半数以上的老人和他们的儿女住在一起,而70%有七八个子女的老人与自己的孩子同住(这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年迈的父母还会定期收到来自儿女(特别是儿子)的经济援助。
如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长期保障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当生育率有所下降时,财政储蓄就会增加。中国政府对家庭规模实行限制政策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实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鼓励生育;1972年,中国政府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阿比吉特及两位出生于中国的合作者——南希·钱(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的独生子)和孟欣(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有三个兄弟姐妹)对储蓄率进行了调查。与1972年之前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1972年之后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平均少要了一个孩子,后者的储蓄率则比前者约高出10%。调查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中国储蓄率的增长幅度达33%(家庭储蓄率从1978年的5%增长到1994年的3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因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对于那些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来说,效果尤为明显,这符合养儿防老的观点。
这一实验虽然有些极端,但影响深远,因为这次家庭规模的缩小范围广,具有突发性及非自愿性。不过,类似的情况在孟加拉国的蒙塔拉伯地区也曾发生过。到1996年,与未普及避孕措施的村庄相比,在普及避孕措施的村庄中,每家每户的各类资产都得到了大幅增加(包括首饰、土地、牲畜及房屋的装修)。一般来说,与对照区相比,实验区每户家庭增加了价值55 000塔卡的资产(购买力平价为3 600美元,是孟加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生育率与儿女交给父母多少赡养费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实验区的父母平均每年从子女那里少收2 146塔卡。
家庭规模与储蓄之间的有力联系,或许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点,即孩子越少并不意味着他们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将来只能得到较低的现金回报,那么他们就需要提前储蓄更多的钱,这会减少他们投资给孩子的钱。的确,如果给孩子投资会比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毕竟养个孩子并不那么费钱)产生更高的回报,那么从长远角度来看,孩子越少,家庭或许会越穷。
同样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父母对女儿会像儿子一样有用不抱希望——比如说,他们需要为女儿结婚准备嫁妆,或者因为女人一旦嫁人,经济就会受制于丈夫——父母对女儿的生活投资会更少。因此家庭不仅会选择要几个孩子最合适,还会选择其性别构成。我们一般认为,生男生女是我们无法决定的,但其实这是错误的:性别选择性堕胎目前十分普遍,而且还非常廉价,父母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堕掉一个女胎。德里主要道路的分路标上,打着(非法)性别选择服务的广告标签:“现在花500卢比,今后节省5万卢比”(嫁妆)。而且,即使在性别选择性堕胎成为一种选择之前,在一大堆儿童病得不到妥善处理的环境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也是摆脱不想要的孩子的一种有效方式。
即使他们的孩子存活了下来,如果父母们偏爱男孩,那么他们或许会一直要孩子,直到生出足够数量的男孩为止。这就意味着,女孩一般都生长在较大的家庭,而且很多女孩都生在那种很想要男孩的家庭。在印度,女婴的母乳喂养期要比男婴短,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喝水的时间较早,可能会更快染上通过水传播的致命疾病,如痢疾等。这是将母乳喂养当成一种避孕措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生下一个女孩之后,父母更可能会早点儿停止母乳喂养,从而增加妻子再次怀孕的可能性。
无论歧视女婴的方式是怎样的,全球女孩的数量过少这一人类生物学始料不及的事实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一篇经典文章中,阿马蒂亚·森计算到,全世界“女性缺口”数量达1亿。这还是在性别选择性堕胎面世之前——自那以后情况越来越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当今的男女比例为124∶100。1991—2001年间(印度最新人口调查时期),印度7岁以下男孩与同龄女孩的比例从105.8∶100上升至107.8∶100。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富裕的三个城邦,而这里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最为严重。2001年,这三个地区的男孩女孩比例分别为126.1∶100、122∶100和113.8∶100。即使根据这些地区自身的报告(其中肯定有“水分”),堕胎的次数也特别多:在有两个女儿的家庭,6.6%的怀孕会以人工流产而告终,7.2%属于“自然”流产。
然而,在女孩更有价值的婚姻市场或劳务市场上,这就不会构成一个问题。在印度,女孩一般不会嫁给本村的人家。通常,大多数女孩都会嫁到距离村子不远不近的地方。结果,当这一婚姻“集中”地区的经济有所增长、更容易找到一个富裕家庭把女儿嫁掉时,我们可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安德鲁·福斯特和马克·罗森茨维格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当一个女孩的婚姻前景更明朗时,男女孩的死亡比例便会下降;相反,村里经济的增长导致男孩的投资价值更大时(因为他们都待在家里),男女孩之间死亡率的差距就会扩大。
针对男孩女孩的相对价值,一个家庭会怎样对待女孩,或许最突出的表现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男女孩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计划农业生产目标针对的是主要农作物。在早期改革时代(1978—1980年),家家户户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包括茶叶和水果。在种茶方面,女人显然比男人效率更高,因为茶叶往往需要用灵巧的手指来采摘。相反,男人在种植水果方面比女人更有能力,因为他们更擅长担负重物。南希·钱指出,当我们对改革前后出生的孩子进行对比时,茶叶种植区域(一般为多雨的丘陵地带)的女孩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更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女孩的数量则有所减少。在并不适宜种植茶叶或水果的地区,农业收入在无任何性别区分的情况下全面增长,孩子们的性别构成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这一切所体现的是,传统家庭的运行中暗含着积极与消极的暴力现象。直到最近,这一现象才开始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总是不愿打开那个藏有真相的“黑匣子”。然而,大多数社会都理解父母们的善意,他们想确保自己的孩子吃饱饭、有学上、懂社交,受到更全面的照顾,但也正是这些父母扼杀了自己小女儿的生命,对此,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切?
在推广自己的那些理论模式时,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家庭与独身一人并不一样。我们将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认为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一个人,一家之主会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决定,如家里该买些什么、谁去上学、上多久的学、谁来继承遗产等。他或许是无私的,但显然是全能的。然而,任何有过家庭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家庭运转模式。这种简化的模式具有误导性,忽视家庭内部复杂的动态变化会产生重要的政策性后果。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给予女性正式的名下财产权对于其生育选择十分重要,这并不会改变她关于生几个孩子的想法,而会使她的想法变得更有分量。
这种最简单的模式忽视了家庭运转方式的重要方面,对这一点的认识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家庭决定被看作是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至少是夫妻双方)谈判的产物。夫妻双方讨论着该买什么、到哪儿去度假、谁应该干几个小时的活儿、生几个孩子,但他们的讨论方式会尽可能地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在怎样花钱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伤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乐,那么他们就会妥协并达成一致。这种家庭观念常常被称为“有效家庭”模式。这种模式让我们认识到,家庭有一定特殊的地方——毕竟,家庭成员并非是因为昨天才见面就被永久地拴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就其所有的决定进行讨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确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家人开了一个小公司(农场或是小生意),他们应始终努力赚更多的钱,以使其他家庭成员获益。
克里斯托弗·尤拉在布基纳法索农村对这一推测进行了验证,那里的每一位家庭成员(丈夫和他的妻子,或几个妻子)都不在同一块地里干活儿。在一个高效的家庭里,所有的投入(家庭劳力、化肥等)都应以使家庭整体收入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到各个不同位置的田地。相关数据也准确地反映出了这一观点。然而,与男性负责耕种的田地相比,由女性负责耕种的田地一般只能分到较少的化肥、男性及儿童劳动力。结果,这些家庭的产量一般都较低。在一块地里用一点儿化肥就能大大增产,但将用量增加到这一原始水平之上并没有多大用处。最有效的是,在每块地里都用一点儿化肥,而不是将所有化肥都用在一块地里。然而,布基纳法索家庭的大部分化肥都用在了丈夫耕种的地里:通过将部分化肥及少量劳动力分到妻子的地里,家庭便可以增产6%而不需额外投入。有些家庭实际上是在浪费钱,因为他们无法就如何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达成一致。
这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很明确:即使同属一个家庭,丈夫地里的产量似乎也决定了他的消费能力,妻子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科特迪瓦,男女有种植不同作物的传统。男人种植咖啡和可可粉,女人种植香蕉、蔬菜及其他粮食作物。不同的作物受天气的影响也不同,降雨量大对于男人的作物来说或许是个好年头,而对于女人的作物来说则是灾年。在与尤拉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埃斯特发现,在男人的好年头里,男人在烟酒及个人奢侈品(如服装的传统饰品)上的消费更大;在女人的好年头里,虽然更多的钱也花在了女人喜爱的小东西上,但她们也会为家里买更多的食物。这些发现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夫妻似乎都不会给对方买“保险”。他们知道彼此将长期生活在一起,丈夫可以在自己的好年头里给妻子买点儿礼物,并在自己的坏年头里得到妻子的礼物。在科特迪瓦,这种非正式的“保险”在同族的家庭之间很常见,但他们为什么不在家庭内部实行呢?
在那里,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在这类家庭中,还有第三个“成员”——不起眼的山药。它既有营养又便于储存,是该地区的一种主食。山药一般是男人种植的作物,但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梅拉苏表示,山药并非是男人可以随意卖掉或吃掉的一种作物。它是一个家庭用于糊口的粮食,只有在需要支付孩子学费或药费时才能卖掉,不能用来买新衣服或香烟。而且,当山药收成较好时,一家人的确会消费更多的山药,这或许并不奇怪,但在购买粮食及教育上的花费也会增加。山药可以确保家里的每个人都吃饱饭、有学上。
因此,家庭的特点并不在于家庭成员间的契合度有多大,恰恰相反,他们会遵循社会承认的简单规则,如“你不应卖掉孩子的山药去买耐克牌衣服”,这种规则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利益,无须为此进行没完没了的谈判。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发现也更有道理。我们看到,当女人在地里的耕作赚了更多的钱,一家人都会吃到更多的粮食。这或许源自梅拉苏所描述的另一个规则:真正负责养家糊口的是女人,丈夫会给她一定量的家用,她的任务就是想出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钱。
因此,家庭成员被一条纽带绑到了一起,但这一纽带并不是高效分享资源及责任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完整的、粗糙的且常常很松散的“契约”,其中规定了每位家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这种“契约”或许需要得到社会的强化,因为孩子无法平等地与父母谈判,妻子也无法与丈夫公平地谈判,但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家庭所有成员对于资源的公平分享。这种契约的不完整性或许反映出了强化较为复杂的事物的艰难性。谁也无法保证父母会喂饱自己的孩子,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社会或许只能对其采取制裁或谴责措施。
靠社会准则对规则进行强化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准则会慢慢地改变,因此那些规则就会面临完全与现实脱钩的危险,有时甚至会带来悲惨的结果。2008年,我们在印尼一个家庭中见到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的家是一座绿白相间的竹楼,旁边还有一间更大的水泥房,那是他们女儿女婿的家,女儿在中东做女佣。这对夫妇显然很穷:丈夫总是在咳嗽,头疼也很严重,因此很难去找工作。不过,他看不起医生。夫妇俩的小儿子从中学辍学,因为家里无力承担他去市里的公共汽车费。还有一个4岁大的孩子,她看上去很健康、营养充足,穿得也很漂亮,脚上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鞋子。这是夫妇俩的外孙女,女儿不在时由他们负责照顾孩子。女儿会寄回孩子的生活费,但没有给夫妇俩赡养费。他们似乎是某种传统准则的受害者——结婚后的女儿不负责赡养她的父母,虽然这明显是不公平的,但祖父母仍然认为有责任照顾他们的外孙女。
尽管家庭中存在很多明显的限制,但社会也并没有提供抚养孩子的其他有效模式。而且,虽然终有一天,社会养老金计划及医疗保险会解放当今贫穷国家的老人,使他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孩子养老,但这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更快乐。政策的恰当地位并不是完成取代家庭的作用,我们有时还应避免政策的滥用。这对如何发挥家庭的功能是极为重要的。
例如,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公共支持计划向妇女提供资金,如墨西哥的PROGRESA计划,这些计划或许有利于将资源分配给儿童。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后,实行了一种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针对那些无个人养老金的65岁以上的男人和60岁以上的女人。在这些老人当中,很多都与他们的儿女及孙子孙女住在一起,家里的钱是公用的。然而,只有在祖母与孙女住在一起时,孙女才会受益——那些女孩一般都发育得很好。但获得养老金的祖父则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只有当女孩的外祖母获得这笔养老金时,这种效果才会显现。
笔者倾向于认为,男人比女人要自私得多。然而,这或许恰恰体现了那些准则与社会期望,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家庭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或许,人们期望女人能将自己获得的意外钱财用来贴补家用,而并不期望男人这样做。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不仅谁挣钱很重要,怎样挣钱也很重要:女人或许还未察觉,她们自己付出劳动所赚的钱“属于”其家庭或孩子。有些矛盾的是,或许恰恰是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公共政策才会倾向于她们。
现在,我们回到穷人是否想建立大家庭的问题上来。帕克·苏达诺想要9个孩子,他的大家庭并非由于缺乏自控力或避孕措施而形成的,也不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一种准则(不过他曾做出的决定或许是基于这样的准则,而他的妻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自己的想法)。同时,他相信,抚养9个孩子使他陷入贫穷。因此,他并非真的想要这么多孩子。他之所以需要9个孩子,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他养老。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他宁愿少要几个孩子,好好地将他们抚养长大,而且他将来也不一定要依赖孩子们。
尽管美国很多老年人都愿意多花一点儿时间,同自己的孩子、孙子孙女在一起(如果电视剧中所演的值得相信的话),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这要归功于社会保险及医疗制度——这种选择对于他们的自尊心及自我认同感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生很多孩子,从而确保将来有人照顾他们。他们想要几个孩子就可以要几个,如果孩子们都不愿或不能照顾他们,公共福利制度则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医疗保险或养老金)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怎样做到这一点。
[1] 总生育率,也叫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不代表妇女们一生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一般以妇女15~44岁或15~49岁为育龄期。——编者注
对 于穷人来说,冒险不可避免,他们常常自己做着小生意,或是经营农场,或是做零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就业保障。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场不好的突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2008年夏,在印尼万隆省的城市贫民区,伊布·蒂娜和她的残疾母亲、两个兄弟及4个孩子(3~19岁)住在西卡达斯的一间小房子里。三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偶尔还会去上学,但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辍学了。蒂娜的两个兄弟都未成家,一个是按日挣工资的建筑工人,另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挣的钱供一家人的花销,但似乎永远也不够交学费、不够给孩子买吃的穿的,也不够照顾生病的母亲。
然而,这并不是蒂娜生活的全部。她年轻时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婚后便帮着丈夫打理服装生意,他们手下曾有4个员工,生意也做得不错。但他们信任的一个生意上的熟人给了他们一张2 0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3 750美元)的空头支票,从此他们的麻烦就来了。他们报了警,而警察却向他们索要250万印度尼西亚盾的好处费,说是给了钱才同意着手调查。付了钱之后,警察的确逮捕了诈骗者,由于这个人承诺偿还欠款,因此只入狱一周便获释了。在偿还了蒂娜400万印度尼西亚盾之后(警察后来又要走了200万),诈骗者承诺将慢慢偿还余下的欠款,但此后他便杳无音信。蒂娜和丈夫交了450万的好处费,却只追回了400万的欠款。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夫妇俩努力工作,试图东山再起,最终通过政府的一个借贷计划,从PUKK贷款了1 5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 800美元)。他们用贷款做起了服装生意,第一批大订单是短裤。于是,他们从服装厂购置了短裤,将短裤熨平并包装好,但这时订购商取消了订单,结果上千条短裤没人要,他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
一连串灾难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巨大压力,在第二次祸事之后不久,他们便离婚了。蒂娜带着4个孩子搬到了娘家,还带去了一大堆短裤。我们见到她时,她仍在努力平复自己内心的创伤,她说自己真的没有精力再做生意了。蒂娜认为,等她觉得好一点儿,她会利用母亲房子的一部分,开一家小的杂货店,或许专卖一些穆斯林节日穿的短裤。
更糟糕的是,蒂娜的大女儿需要特殊的照顾。4年前,大女儿曾遭到绑架,绑架她的是住在她家旁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人几天后便放了她,但大女儿因此留下了心理阴影,从此便待在家里,既不去工作也不去上学。
蒂娜是否太倒霉了?从某种程度上看的确如此。她认为,女儿遭到绑架是一次意外事件(不过这还与她们家离铁路很近有关,那里常常住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但她同样坚信,她生意上的厄运其实就是那些小企业主生活的写照。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此外,穷人常常要为他们自己的生意筹集所有资金,这些资金要么来源于家里的积蓄,要么是从别处挪借的,而这种情况是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面对的。
很多穷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或农场。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平均50%的城镇穷人从事着非农业工作,而从事农场生意的乡村穷人在25%~98%之间(南非是一个例外,黑人人口有史以来一直被排挤在农业之外)。此外,很多这样的家庭也做非农业生意。而且,大部分由穷人耕种的土地都缺乏灌溉,这使耕种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一场旱灾或是雨下得迟一点儿,都会导致未经灌溉的土地农作物歉收,半年的收入也成了泡影。
并非只有业主或农场主才需要承担收入风险。对于穷人来说,按天计算工资的零工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农村地区极度贫穷的人之中,半数以上是这样的零工。在城镇地区,零工的比例约为40%。如果这种零工够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建筑工地或农场找到能持续几周或数月的工作,但通常只能找到几天或几周的工作。零工永远都不知道,手头的活儿干完之后还能不能找到别的活儿。如果生意上出了问题,这份工作立即就会消失,比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帕克·索林,他没过多久就失业了,其原因在于化肥价格和油价的上涨,以及农民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因此,与固定工人相比,零工的工作日更少,很多零工一年也干不了几天活儿。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项调查发现,零工平均每年工作254天(上班族为354天,个体户为338天),1/3最底层的零工只工作137天。
农业领域的大灾难,如1974年孟加拉国的旱灾(工资相对于购买力下降了50%,而且据估算,多达1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还有非洲的粮食危机(如尼日尔2005—2006年的旱灾),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即使是在正常年份,农业收入每年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孟加拉国任何一个正常年头,农业工资可以高出或低于其平均工资水平的18%。而且,国家越穷,这种变数就越大。例如,印度农业工资的变化幅度是美国的21倍。这并不奇怪:美国农民都有保险,他们可以获得补贴,并受益于规范的社会保险计划;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头,他们也不需要解雇自己的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
变化莫测的因素还不只这些,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很大。2005—2008年,粮食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这一价格彻底瓦解,过去两年来只是涨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高粮食价格原则上会受到生产者(农村穷人)的欢迎,却会伤害到消费者(城镇穷人)。然而,2008年夏,粮食及化肥的价格都破了纪录。与我们在印尼和印度交谈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快撑不住了:农民们认为,成本涨得超过了价格;工人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农民们都在省钱;同时,城镇居民几乎买不起粮食了。问题并不仅在于价格水平,而是这种不确定性。例如,农民要花很多钱买化肥,但他们无法确定,农作物丰收时的价格是否还能保持较高水平。对于穷人来说,风险并不仅限于收入或食品,我们在前一章谈到的健康问题也是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政治暴动、犯罪(如伊布·蒂娜女儿的案例)及腐败的问题。
穷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风险。矛盾的是,有些事件在富裕国家被认为是灾难性的,但这些事件似乎很少在这些国家发生。2009年2月,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警告全球首脑们:“全球经济危机将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危机,除非他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尽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专注于拯救银行及激励方案,我们不应忘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穷人,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变动,那些穷人受到的影响会大得多。”世界银行发言人在谈到这一主题时还说道,随着全球需求的下降,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建筑工地的零活儿,以及他们在工厂里的工作。由于缺乏外部援助,并伴随着税收减少的压力,穷国政府将会削减对学校、健康设施及援助计划的预算。
2009年1月,我们和索米妮·森古普塔——当时《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来到印度孟加拉邦玛尔达农村地区。她想写一篇关于全球危机怎样影响穷人的报道。森古普塔生长在加利福尼亚,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孟加拉语。别人告诉她,德里很多建筑工地的大量工人都来自玛尔达。而且,森古普塔了解到,德里的建筑业发展得很慢。因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问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迁移经历是怎样的。
每个人都认识迁移过来的人。很多人是为了回家过穆哈兰姆月 [1] ,印度很多的穆斯林都过这个节。每个人都很乐意和我们谈起他们的移居经历。很多母亲告诉我们,印度南部或北部的一些遥远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如卢迪亚纳、哥印拜陀和巴罗达,他们的儿子和侄子目前就在那儿生活和工作。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悲惨的经历——一个女人谈起,她儿子因患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死在了德里——但她的口吻却很乐观。森古普塔问:“市里能找到工作吗?”“是的,市里有很多工作机会。”“你听说过裁员吗?”“没有,孟买没有发生裁员,一切都很好”……我们还来到了火车站,想看看是否有人因丢掉了工作而返乡。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三个正赶回孟买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从没来过孟买,其余两个人都是老手,他们向那个没来过孟买的人保证,他一定能在这儿找到工作。直到最后,森古普塔也没写出穷人如何受到全球经济萎缩影响的文章。
关键并不在于,孟买的建筑工作在危机时期没有减少——有些工作的确减少了——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机会。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工资是在村里干活儿的两倍多。相对于他们的痛苦经历——每天都担心找不到工作——流动建筑工人的生活似乎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然,全球经济危机的确增加了穷人的风险,但对于他们每天需面对的全部风险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即使没有令世界银行担心的全球危机,情况也会是这样。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贬值75%,粮食价格上涨250%,国民生产总值下跌12%。然而,种植大米的农民(一般是最贫穷的人群之一)实际购买力却提高了。只有政府雇员及工资相对固定的人,才陷入了糟糕的境地。1997—1998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经济下滑10%。即便如此,在接受调查的约1 000人中,2/3的人表示,他们的工资下降主要是因为一场旱灾。只有26%的人说主要原因是失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失业并不是完全由这场危机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穷人来说,事情似乎并不比往年更遭,因为他们的境况一直都很糟。他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熟悉的问题。在穷人看来,每一年都过得像身处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一样。
穷人不仅过着风险更大的生活,而且同样一场灾难,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首先,对于手里本来没有几个钱的人来说,削减消费是极为痛苦的。如果一个不太穷的家庭需要削减消费,家庭成员或许就要少打电话,少买点儿肉,或是将孩子送到更便宜点儿的寄宿学校。显然,这都会令人感到痛苦。但对于穷人来说,大大削减收入可能就意味着一些必要开销的削减:去年,我们在乌代布尔农村地区对一些极度贫穷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其中45%的成年人常常吃不饱饭。这是穷人最憎恨的一件事:与那些能吃饱饭的被访者相比,吃不饱饭的被访者表示,他们过得很不快乐。
其次,当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呈S形时,与目前的不愉快相比,一场灾难对于穷人的影响或许会更糟。在图6–1中,我们画出了印尼女商人伊布·蒂娜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的关系。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对于几乎没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说,如果投资回报相对较小,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而对于投资能力较高的人来说,投资回报也会更高。伊布·蒂娜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个案例中,明天收入与今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因为她的生意要具备赢利所需的基本规模(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这是穷人做生意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她的情况很常见)。在灾难之前,她和丈夫手下有4个员工,有足够的钱购买原材料,雇用员工制作服装,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模式。在这之后,他们能做的只是买进成品短裤并进行包装,这种生意相对来说不怎么赚钱,或者根本就不赚钱。在支票被退回之前,伊布·蒂娜和她的丈夫处于“贫穷陷阱”之外。如果跟随他们的轨迹,我们会看到,他们正沿着最终实现高收入的轨道前进。然而,那场灾难卷走了他们全部的资产,并使他们掉进了“贫穷陷阱”。后来,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穷:当我们见到伊布·蒂娜时,她已经沦落到需要靠她兄弟的接济生活的地步。因此,这一“S”形世界的一场灾难会产生永久性后果。如果今天收入与明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这个家庭便会脱离通往中产阶级之路,转而踏上永久贫穷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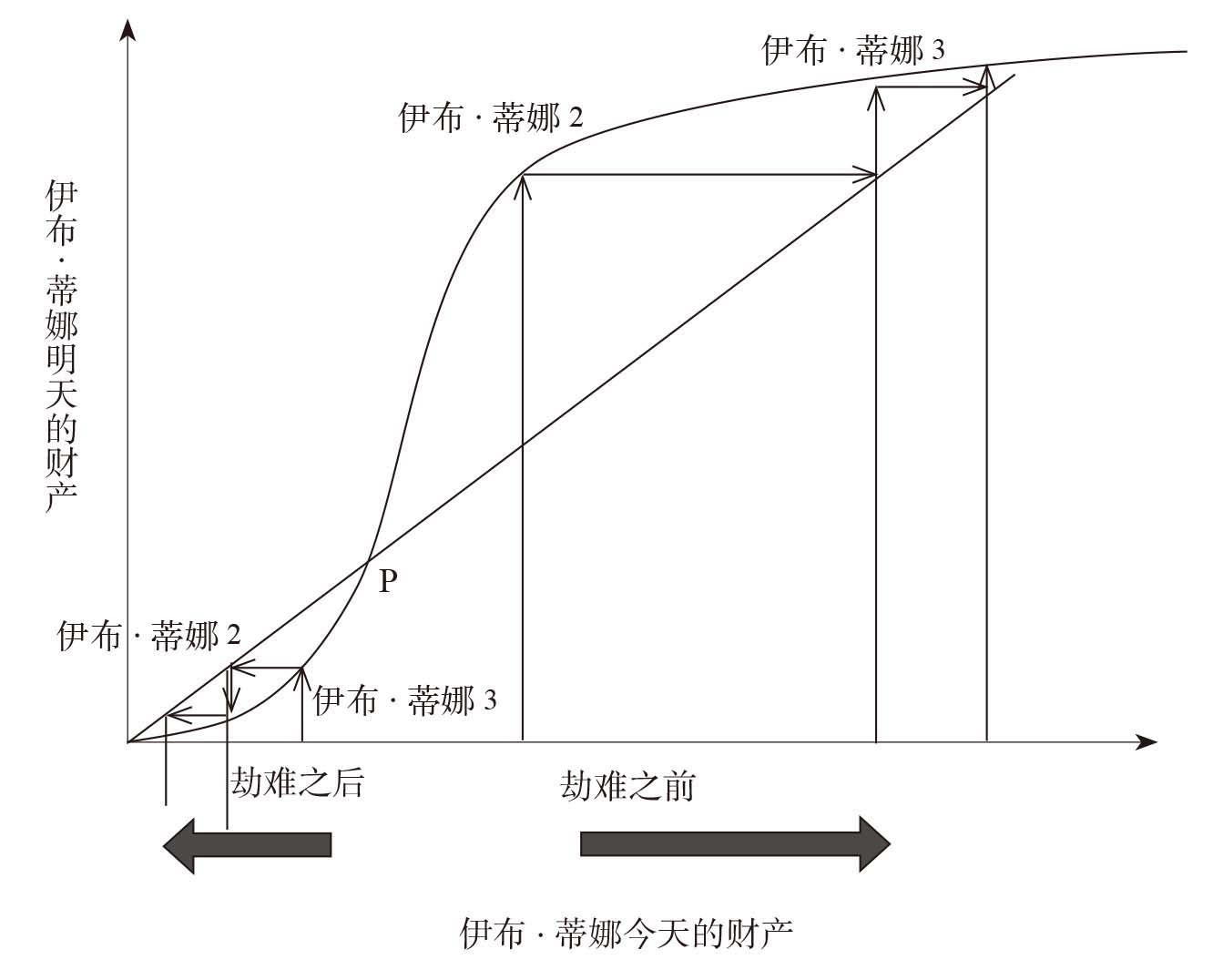
这种情况常常会受到一种心理过程的强化。失去希望,感到没有出路,这会大大降低人们渡过难关所需的自控力。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帕克·索林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曾在农场工作,但现在只是偶尔钓钓鱼。伊布·蒂娜也是一样。他们似乎都不具备振作起来、从头再来的心理素质。我们在乌代布尔见到了一个人,他在回答一个标准的调查问题时说,他曾经感到“担忧、紧张和不安”,这甚至影响了他一个多月的日常活动,如睡觉、工作和吃饭。我们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他的骆驼死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哭泣,并总感到紧张。我们接着问他,是否曾想办法治疗这种抑郁症(比如找朋友、医疗保健人员或传统医生谈谈心),他似乎很不耐烦地说:“我失去了我的骆驼,当然会伤心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种影响或许还来自其他一些心理因素:面对风险(不仅包括收入风险,还有死亡或疾病的风险)会使我们为此担忧,而担忧会给我们带来压力,产生抑郁情绪。在穷人当中,抑郁的症状更为普遍。我们在感到压力时更难集中注意力,这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贫穷与身体所分泌的皮质醇水平密切相关,因为皮质醇水平标志着压力的大小。相反,当家庭成员接受某种援助时,他们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有所下降。例如,与母亲未接受墨西哥现金转移计划的孩子相比,受益于该计划的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低得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及决策能力。由压力释放的皮质醇会影响大脑的部分区域,如前额皮质、类扁桃体、海马区,这些都是认知功能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前额皮质,该区域对于抑制冲击响应很重要。因此,将实验对象置于实验室的压力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经济选择时,他们不太可能会做出理智的决定。
穷人怎样应付这些风险呢?在面临工资或收入下降时,穷人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增加工作量。然而,这有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在时局不好时(例如一场旱灾或成本价格上涨),所有的穷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他们会相互竞争,导致工资水平进一步下降。如果他们不能在村外找到一份工作,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严重。因此,在印度那些较为封闭的村庄里,劳力们更难走出去寻找工作,同一类旱灾会对这里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在这些地区,在解决工资降低的问题上,增加工作量并不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如果灾后增加工作量并非一个好选择,那么最好的办法常常是,通过业务多元化来缩小风险范围,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很明显,穷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智慧。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穷人选择了多样化的活动,而不是金融工具。一个关于穷人的显著事实就是,一个家庭似乎会涉足多种职业:在对孟加拉邦27个村庄展开的一项调查中,即使那些声称以耕作为生的家庭,也只是花了40%的时间从事耕作。调查中的一般家庭都有三个成员在工作,涉及7种职业。尽管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但这往往不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方式。这可能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如果一项活动赔了钱,其他活动还能让他们维持生计。不过,我们将看到,这其中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在一个村庄的不同位置有很多块地,这也会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散。当村里的一个区域遭受病虫害时,其他区域则可能安然无恙;如果不下雨,在更容易吸收地下水的地里,庄稼存活的概率更大。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同一村庄的不同区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小气候,这是由暴露程度、坡度、高度及湿度所决定的。
临时性迁居也可以从这一层面来加以解释。一家人全都迁居城里较为少见。通常情况下,选择迁居的家庭成员大多为印度或墨西哥的男人或十几岁男孩,还有中国、菲律宾及泰国的女孩,其他人则留在家里。这可以确保一个家庭的财富并未全都押在去城里工作的人身上,还可以保持这个家庭在村里的人际关系。我们将看到,这种人际关系常常是非常有用的。
穷人降低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保守地经营他们的农场或生意。例如,他们或许知道有一种新型农作物的产量更高,却不去耕种这种作物。固守传统方法的一个好处就是,农民不需要去买新的种子,他们可以再种植上个季节省下来的种子——新种子常常要花费很多钱。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农民们能赚到几倍于投资新种子的钱,但作物歉收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比如不下雨),到那时,农民就会赔掉用来买新种子的额外投资。
家庭还会利用一些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印度的农户利用婚姻作为一种分散大家庭“风险组合”的方式。一个女人婚后搬到婆家所在的村庄,娘家与婆家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纽带,在遇到麻烦时,两个家族便可以寻求对方的帮助。农户一般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村庄,既方便与亲家建立关系,气候格局又不会完全相同。这样一来,如果一个村庄受灾,另一个村庄没受灾,他们就能向对方伸出援手。另一种保险的方式或许就是,生很多个孩子。别忘了,帕克·苏达诺有9个孩子,就是为了保证至少有一个能为他养老。
穷人应对风险的所有方法一般都很昂贵。在农业领域就有很好的证明:在印度,有些贫穷农民住在年均降雨量不太正常的区域,他们利用农业投入来获取利润的方式较为保守,且效率较低。如果这些农民住在年均降雨量可预测的地区,那么他们的利润率就会上涨35%。此外,受这种风险影响的只有穷人;对于较为富有的农民来说,农作物利润率与雨水变量之间并无关联,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承担得起作物歉收的损失,因此他们愿意承担这份风险。
贫穷农民常常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做某人的佃农。也就是说,地主支付部分耕作成本并收取部分成果。这种方式以激励为代价降低农民风险:由于知道地主将拿走地里所种任何作物的一部分,农民努力工作的热情就会减少。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享有自己地里作物所有权的农民相比,佃农所付出的耕种热情将减少20%。结果,这样的土地耕种得较为粗糙,利用率也较低。
很多穷人都身兼数职,但这同样是缺乏效率的。如果不够专业的话,他们很难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在城市里,有些女人会涉足三种不同的职业,而有些男人却无法专注于一项工作,因为他们想每隔几周就回到村里。这些人会放弃学习其主业方面的技能及增加经验的机会,进而错失专门从事其擅长领域的收益。
因此,一旦遭受某种冲击,穷人不仅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担心坏事的发生,他们充分认识自己潜力的能力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另一个处理风险的方式是,村民们相互帮助,渡过难关。大多数穷人都住在村庄或社区中,他们有一个范围广泛的熟人网络:基于宗教或种族的大家庭及社区。尽管有些灾难会影响到关系网中的每个人,但有些困难则更为具体。如果目前处境好的人帮助了有难处的人,那么当前者有难处时一样可以得到对方的帮助,这样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助人为乐并不仅限于慈善机构。
在克里斯托弗·尤拉所做的一项调查中,这种非正式保障的成效与局限得到了体现。尤拉在尼日利亚乡村地区住了整整一年,他让村民们记录下互相馈赠的每件礼物或每笔非正式借款,以及还款的具体条件。每个月,他都会问村民们是否发生过什么坏事。他发现,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个普通家庭都与平均2.5个其他家庭存在借贷关系。此外,贷款条件会根据借贷双方的情况进行调整。当借款人遭遇一次灾难时,他会偿还得少一些(通常少于原始借款量),但如果贷款人遇到难事时,借款人实际上会偿还比借款更多的钱。对于减少每个人所面对的风险,这种密集的相互借贷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非正式互助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使关系网中所有人的总收入没有改变,但在有些家庭遭遇一次灾难时,他们仍然需要缩减开支。
一个较大的研究机构对这一非正式保险现象进行了调查,通过对科特迪瓦、泰国等一些国家的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尽管传统的互动网络的确有助于分摊灾难的影响,但这种网络所提供的保障并不是完美的。如果风险有了很好的保障,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就应根据其平均收入能力而定,始终保持一个大致的水平:在一个家庭处境不错时,它会帮助别的家庭;而在其境况不好时,别的家庭也会帮助它。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特别是健康危机,穷人在这方面极度缺乏保障。在印尼,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得了重病,那么这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就会下降20%。一项在菲律宾展开的研究表明,在涉及非致命重病的情况下,村庄内部的互助程度非常糟糕。当一个家庭收成不好或家里有人失业时,村里的其他家庭会向其伸出援手。遭遇困境的家庭会收到礼物、无息贷款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然而,当个人患上某种疾病时,情况显然就大不相同了,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家庭应对此负责。
这种医疗保障的缺乏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各个家庭的确在其他方面相互帮助。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伊布·艾姆塔特,她是我们在爪哇岛一个小村庄见到的女人,她的丈夫患有眼疾,孩子不得不辍学,因为她负担不起治疗孩子哮喘病的医疗费。伊布·艾姆塔特向当地放债人借了1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75美元),用于支付丈夫眼疾的医疗费。当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欠款100万印度尼西亚盾了(加上逐渐增多的贷款利息)。她非常担心,因为放债人威胁说,如果她还不起钱,就要拿走家里所有的东西。然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她的一个女儿刚刚给了她一台电视机。女儿自己刚刚花8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50美元)买了一台新电视机,于是决定将那台旧的(仍然很好用)送给母亲。我们有些惊讶:如果女儿留着那台旧电视机,给父母一些钱还款,这不是更合理吗?我们问艾姆塔特:“难道没有一个孩子能帮忙还款吗?”她摇了摇头,回答说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家——她的意思是说,她不愿孩子们以馈赠的形式帮助她。她似乎认为,没有人帮她解决医疗费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人们不向彼此提供更多帮助呢?为什么某些风险未得到很好的规避呢?
对此,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或许我们不愿向朋友或邻居提供无条件的帮助。一方面,我们或许会担心,保证向某人提供帮助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惰性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或者,人们可能会在没有必要时提出需求。或者,相互帮助的许诺并未真正实现:我帮助了你,但轮到你帮助我时,你却总是在忙别的。
我们为何会不愿帮助别人?这方面的解释似乎有很多。但我们尚不清楚,这是否可以解释不去帮助那些病重的人,因为患病并非一种选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正式保险来自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之所以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日后可能也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或许我们会在紧急关头向邻居伸出援手,但当时我们可能并没想过自己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这可能仅仅是出于看到邻居挨饿而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贝奇·哈特曼和吉姆·博伊斯合著了一本关于孟加拉国农村生活的书,书中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书中描述了互为邻里的两个家庭,一个信仰印度教,一个是穆斯林,两家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印度教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因此一家人都在挨饿。出于绝望,这个家庭的女人常常越过栅栏,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偷点儿能吃的树叶。而那个穆斯林家庭知道这一切,但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穆斯林家庭的男人说:“我知道她的人品并不坏,如果我陷入了她那样的处境,我可能也会偷东西的。当我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时,我会努力做到不生气。我总想:拿走东西的人一定比我更饿。”
人们会在彼此遇到难处时互相帮忙,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并不是他们盼望着将来能得到回报。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正式的关系网不具备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即使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如果家里还有饭吃而邻居却在挨饿,他们也会给邻居一口吃的。然而,帮助别人支付医疗费用这类情况已经超出了互助行为的界限:鉴于医疗费用极为昂贵,很多家庭将不得不因此倾家荡产。因此,将健康问题列在助人为乐的基本道德责任之外,还是说得通的。因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更高的社会契合度。
互助保险是一种助人为乐的道德责任,这种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尼日利亚的一些村庄,村民们助人为乐都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大家都去帮助一个对象,虽然以后面这种方式分摊风险会更有效。这或许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伊布·艾姆塔特的女儿给了母亲一台电视机,却没有帮她支付医疗费。她不想为父母的健康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指望其他兄弟姐妹能慷慨解囊。因此,她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她的父母做一点事情。
鉴于非正式互助网络的保障有代价高昂的风险及局限性,我们肯定会想,为什么穷人没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正式保险,也就是由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然而,任何形式的正式保险在穷人当中都很少见。医疗险、坏天气险,还有牲畜死亡险,这些都是富裕国家农民生活中的标准保险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多多少少是欠缺的。
既然小额信贷是人人皆知的,对于高尚又有创意的资本家来说,穷人的保险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机会目标(《福布斯》专栏称之为“穿不透的自然市场”)。穷人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如果保险费用合理的话,他们应该愿意为自己的生活、健康、牲畜或庄稼投一份保。几十亿穷人都在等待着投保,即使每项政策只有微薄的利润,这也是一桩大买卖。同时,这也会为全球穷人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一切似乎只缺少某个组织这一市场的人。因此,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及大型基金会(例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资了数亿美元,鼓励穷人参与投保。
当然,这种保险的提供显然存在很多难处。这是一些基本问题,并不仅限于穷人,但在贫穷国家较为突出,因为它们很难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管理,也很难对被保险人实行监督。我们已经提到过道德风险:一旦人们知道自己无须承担全部后果,他们就可能会改变其行为(不那么认真耕种、在医疗方面花更多的钱等)。以医疗保险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穷人也总会去拜访不同类别的医疗从业人员。如果能够免费看病的话,他们会怎样呢?医生是否还有理由让病人做一些不必要的化验、为其开一些不必要的药品——特别是在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的情况下(美国和印度的很多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到药店去拿提成?一切似乎都表明:病人想看到行动,因此他们更喜欢会开药方的医生,而医生开的药越多,挣得就越多。在卫生保健服务管理不善的国家,任何人都能以“医生”的身份开家药店,为门诊病人提供基于报销制度的医疗保险,这似乎是他们走向破产的第一步。
另一个问题是“逆向选择”。如果保险是非强制性的,那些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出问题的人,参保的概率或许更大。这也无所谓,只要保险公司清楚这一点即可,因为这可以折算成额外的费用。然而,如果保险公司并不能确定人们是否因目前需要而参保,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提高每个人的投保费。不过,更高的费用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会赶走那些觉得自己将来可能不需要保险的人。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因此,在美国,人们很难以合理价格参加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为员工投保。所以,价格合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一般都是强制性的——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参保,保险公司就不会承担高风险。
第三个问题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怎样防止医院给保险公司提供大量虚假索赔证明,或收取病人不必要的医疗费?而且,如果一位农民为自己的一头水牛投了保,怎样才能防止他谎称自己的水牛死了?印度工业信贷投资基金会的纳奇凯特·摩尔和宾杜·安纳斯来自印度的同一金融部门,该部门主要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他们略带自嘲地对我们讲,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灾难性的尝试是提供牛险:首先,一大堆投保人都声称自己的牛丢了。于是,他们决定,要想索赔死去的动物,主人必须提供死牛的耳朵。结果繁荣了牛耳市场:任何死去的牛无论投保与否,耳朵都会被割掉并卖给那些投保牛险的人。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得到索赔,又保留着自己的牛。2009年夏,在我们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印度IT巨头印孚瑟斯公司创立者、前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对其独特身份认证的计划进行了说明,因为政府一直要求他为每个印度人提供一种“独特身份证”。他向听众们保证,只需10个指纹及一张虹膜照片,就足以准确地对每个人加以认证。摩尔听得很认真,当尼勒卡尼停顿时,摩尔突然说:“太遗憾了,牛没有手指。”
某些险种比较容易投保,例如天气。如果附近气象台测量的降雨量在特定水平之下,农民就应估算一下保险公司支付给他的钱款数量(根据他所支付的保险费)。由于没有人能控制天气,而且人们无法判断该为此做些什么(不同于医疗的情况,人们必须决定需要哪种化验或治疗),因而不存在道德风险或欺骗行为。
在医保范围之内,为灾难性健康问题投保(重大疾病、事故),似乎比为门诊病人支付费用更容易。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想做手术或化疗,而且治疗与否很容易得到验证。虽然过度诊治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保险公司可以就支付哪项治疗费用设限。但这仍然存在一个大问题,即保险公司并不想只有病人来投保。
避免逆向选择的技巧就是,找到出于健康之外的原因集中来投保的目标人群——一家大公司的员工、小额信贷客户、公费医疗者……尝试着让他们参保。
正因为如此,很多小额信贷机构(MFI)想到了提供医疗保险的方法。他们有大量的借款人资源,可以向这些人销售保险产品。而且,由于重大疾病问题,有时原本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客户也会变成违约者,小额信贷机构投保也将因此承担一定的风险。此外,向客户收取保险费会很容易,因为贷款负责人每周都会与他们见面——实际上,他们可以将保险费折算到贷款中。
2007年时,SKS小额信贷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该机构引入了一种名为“Swayam Shakti”的试点医疗保险计划,涉及生育险、住院治疗险及意外事故险。为了避免一些群体进行逆向选择,SKS强制为他们投保该计划。为了解决潜在的欺骗问题,投保收益范围被设限,该计划鼓励客户们前往那些与SKS有长期关系的医院。为了使其更加人性化,去这些医院的客户们获得了一种“无现金工具”:只要他们的治疗涉及一种投保疾病,他们就无须支付费用——SKS会直接向医院支付。
当SKS开始引入这一保险产品时,该公司尝试着强制客户投保。但由于客户提出了抗议,SKS决定只在首次延期时进行强制性投保。结果,有些客户决定不再延期贷款了,于是SKS逐渐失去了提供该保险地区的客户。几个月之后,SKS贷款延期率从60%左右降至50%左右。另一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问起我们与SKS的合作时,我们回答说正在评估强制性医疗险对小额信贷客户的影响,这位首席执行官听后笑着说:“哦,这我了解!SKS在哪里推出这种强制产品,我们在哪里的客户就会增多。人们都离开SKS加入了我们的机构!”约1/4的客户想继续从SKS借款,但他们又不想参保,于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漏洞:他们在一年期保险快要到期之前预付贷款。这样一来,当他们延期贷款时,他们仍然巧妙地处于投保期之内,因此不必支付更多的保险费。针对客户的这一手段,SKS决定将这一保险产品变成自愿性的。然而,只有少数客户自愿投保,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次出现。用于每位投保客户的费用迅速增长,由于处于亏损状态,代表SKS提供保险的印度工业信贷伦巴德保险公司决定,要求SKS停止接受新的投保客户。其他一些试图推出类似计划的组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客户抗议强制性投保。
小额健康保险并不是唯一遇到麻烦的险种。包括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罗伯特·汤森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对一种简单天气险的影响进行评估。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险种类似,当降雨量少于特定水平时,保险公司会支付一定数量的理赔金给客户。这种产品在印度有两个销售区——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都是干旱少雨的地区。在这两个地区,该产品通过一家知名的小额信贷组织进行销售。该组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为农民提供并赠送保险服务。总的来看,签约率依然很低:最多只有20%的农民购买了某种保险,而且只有在这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工作人员上门销售时,才能达到这一签约水平。此外,即使买了保险的人也没买多少:如果不下雨的话,大多数农民所买的保险只能弥补其2%~3%的损失。
投保需求低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破坏了这一市场。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需求达人的观点:当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或国际机构的供应过大可能就会受到指责。具体而言,当灾难降临时,那些善良的灵魂会伸出援手,因此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保险。
在发生大暴雨的年头,印度一些地区争相想被定为“旱灾区”,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援助。在政府的建筑工地上,人们可以找到工作、分到食物等。但有一点我们应明确,这不过是穷人需要的一小部分。一方面,政府只在大灾发生时才会进行干预,而不会去管一头牛死了或某人被车撞了这类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救灾物资分发到穷人手中也不够及时。
另一种可能性是,穷人对保险的概念并不是很了解。的确,保险与穷人接触过的大多数交易并不一样。保险是你预先支付一定费用,为将来生活购买的一种保障,但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用到。我们在与SKS客户交谈时遇到了很多人,即使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没有遭遇过祸事,当他们的医疗保险费不能报销时,他们仍然感到很沮丧。我们当然可以将保险的概念解释得更清楚,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能够巧妙地发现SKS系统中的漏洞,却搞不清楚保险的基本原理。为了销售天气险,汤森想弄清楚人们是否了解保险的运行方式,于是对此做了一个实验。在拜访每一位农民时,销售人员会大声地向他们简要介绍一种假想的保险产品(温度险),然后向潜在客户提出几个假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这种保险怎样生效的。被访者答对问题的比率为75%。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普通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否能做得更好。因此,毫无疑问,将天气险解释得更清楚,对于农民购买保险的意愿并无影响。
农民能够理解保险的核心概念,以及保险是怎样运行的,他们只是对买保险不感兴趣而已。然而,他们还是会考虑买点儿小东西。在没有任何销售努力的情况下,一次简单的家访会将购买天气险的人数提高四成。在菲律宾,有些家庭被随机挑选出来,完成一份基本调查,其中包含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相对于未填写基本调查的对照家庭,他们最终更有可能会购买医疗险。据推测,回答健康方面的问题提醒了他们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即使没有这些小点拨,鉴于发生问题的概率也很高,穷人为什么仍对保险的好处置若罔闻呢?
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问题,市场所提供的险种只覆盖了灾难性的情况,这就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可信度始终是保险产品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保险合同要求一个家庭预付一些钱,而他们将来能否得到补偿则是由保险公司决定的,所以这个家庭一定要完全信任该保险公司。以天气险为例,产品销售小组有时会与来自贝司克斯的人一起——贝司克斯是农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组织——有时则单独开展工作。他们发现,与贝司克斯的人一起时,签约率会受到很大影响,这表明信任是一个问题。
遗憾的是,这种可信度的缺乏或许是一种地方病,它取决于产品的性质,以及保险公司应对任何欺诈可能的方式。2009年冬,我们访问了SKS的一些客户,这些客户已决定不再续订医疗险。一位女士说,她去医院看胃病,但后来SKS拒绝给她报销,因此她决定不再续订该保险了。由于该险种只覆盖灾难性问题,胃病虽然很可怕,却并不在报销范围之内。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种区分——毕竟,她去了医院并在那接受了治疗。她还谈到一位购买了另一种保险的女士,这位女士的丈夫死于一种严重的疾病,但她在丈夫去世前还是花了大笔的医疗费。丈夫去世后,她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理赔要求,但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理由是她的丈夫从没住过院。很多女士都被这件事吓坏了,于是她们都决定不再支付保险费。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显然有权拒绝理赔。但另一方面,还有什么事会比这更具灾难性呢?
天气险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问题。庄稼可能会枯死,农民可能会挨饿,但如果气象站所测量的降雨量在标准之上,那么该地区就没有人能得到理赔金。然而,还有很多局部气候:在地区平均降雨量在旱灾线之上的年头,很多农民必须承受与灾难几乎相同的损失,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腐败现象很普遍的情况下,让受难的农民接受气象台的定论并不容易。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不一致,这方面我们已在前文谈过。在决定是否买保险时,我们需要现在付出行动(支付保险费),但回报却发生在未来。这是人类不太擅长的一种推理类型。当保险只覆盖灾难性问题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处理了:回报会发生在未来——一个特别不愉快的、谁也不愿去想的未来。不去花太多时间预测这些事件,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这或许也能说明,人们为什么在答完问卷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时,才更有可能会去买保险。
出于这些原因,小额保险或许不会成为下一个拥有10亿客户的市场机制:对于市场愿意提供的某些保险产品,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这似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穷人显然要为此承担难以接受的风险。
因此,政府需要扮演一个明确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取代私人保险市场。但要让一个真正的市场出现,政府必须挺身而出。私人公司可以继续销售其正在销售的险种(有严格限制的灾难险、基于指数的天气险等)。但就目前来说,政府应为穷人支付部分保险费。已有证据表明,这是行得通的:在加纳,当农民享受很大一部分天气险补贴时,几乎所有农民都会购买这种保险。因为对灾难的恐惧会使穷人采取昂贵的缓解对策,保险补贴费用可以由农民的额外收入自行抵消。与未接受廉价保险的农民相比,接受这一保险的农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庄稼施肥,因而会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吃不饱饭的可能性也变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看到保险的好处,感受到这一市场的繁荣,那么保险补贴或许就可以取消了。即使没有这种可能性,只要穷人无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对冲基金经理,并因此而实现巨大的潜在利益,这似乎也是一个利用公共资金促进共同富裕的好方式。
[1] 穆哈兰姆月,意为“圣月”,是伊斯兰历的第一个月,相当于其他历法中的元旦。本月不许打斗。——编者注
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无数水果及蔬菜摊贩站在街角。每个摊贩(常常是女人)都有一个铺着一层帆布的小推车,上面摆着西红柿、洋葱或是她们碰巧正在卖的任何东西。摊贩们早晨从批发商那里进货(常常是以赊账的方式),然后卖一天的货,晚上将欠款偿还给批发商。有时,他们用来装菜、卖菜的推车也是按天租用的。
在很多富裕的国家,这也是商人做生意的方式:他们获得营运资本贷款,用于生产或购买货物,然后用他们的收入支付贷款。很明显,与富人相比,穷人需要偿还的贷款数额要多。在印度陈耐市,如果水果贩早上从批发商那里进了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的蔬菜,那么她晚上平均需偿还批发商1 046.9卢比。支付的利息为每天4.69%。要想搞清个中原因,我们可以先来计算一下:如果你今天借了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那么你明天就要偿还104.69卢比,如果你延迟一天还款,那么后天你就要偿还109.6卢比。如果借款30天,你就欠了近400卢比;而如果借款长达一年,应还款就高达1 842 459 409卢比(购买力平价9 350万美元)。因此,一份5美元的贷款,如果贷款期长达一年,这一债务将接近1亿美元。
这一高额利率呼吁着小额信贷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例如,帕德马贾·蕾迪是斯潘达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她告诉我们,她创立该公司的灵感来源于一场谈话,谈话对象是安得拉邦贡土尔市一个拾破烂的人。蕾迪意识到,如果拾破烂的人拥有能买一辆推车的钱,那么,她就无须支付日租金了。省下来的钱,她在几周内就能买到很多推车。不过,那个拾破烂的人并没有能买得起一辆推车的钱。蕾迪问自己:“为什么没人借给他买一辆推车的钱呢?蕾迪说,拾破烂的人给出的解释是,银行不会借钱给他这样的人。他可以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但借款的利息非常高,根本行不通。最终,蕾迪决定借钱给这个拾破烂的人。他如约还清了欠款,很快发达了起来。不久,蕾迪家门口前来借款的人排起了长队。于是,蕾迪决定辞职并创立斯潘达纳公司。13年后的2010年7月,斯潘达纳公司已拥有420万贷款客户,涉及贷款额高达420亿卢比。
穆罕默德·尤努斯被誉为“现代小额信贷之父”,他的观点与蕾迪大致相同:银行不愿与穷人接触。很多意图谋利的放债人和生意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向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任何人只要不以搜刮穷人为目的,都可以进入这一市场。他们只向穷人收取一点点足以维持运营的利息,或者稍稍赚取一点儿,但不会很多。由于复利的作用,利息稍微下调就能改变客户的生活。以水果商贩为例,假如他们借到了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即使贷款利息很高(比如每月10%),他们也可以用现金买进蔬菜,而不是赊账进货。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少付给批发商4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203美元)的利息,这笔钱足以偿还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只需几个月就能将生意做大,并摆脱贫穷。
然而,这一简单的情况也会产生问题。陈耐市有很多水果批发商,为什么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或是一位有创意的放债人)不稍稍降低利息呢?这样,它就能一直占领整个市场,并保持一定量的盈余。为什么水果商贩要等待穆罕默德·尤努斯或帕德马贾·蕾迪这样的人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倡小额信贷的人有些过于保守:在出现垄断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对于小额信贷消除贫穷的潜能,他们或许有些过于乐观。虽然在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水果小贩变成水果巨头的奇闻,但陈耐市仍然有很多贫穷的水果商贩。即使他们所在城镇中有很多小额信贷机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不会向这些机构借钱。难道他们放弃了摆脱贫穷的机会?还是小额信贷并非像我们听说的那样神奇?
穷人很少向正规贷款机构借钱,比如商业银行或合作社。我们在印度乌代布尔农村地区的调查中,约2/3的穷人都借过钱。其中,23%是向亲戚借的,18%是向放债人借的,37%是向店主借的,只有6.4%是通过某种正规渠道借的。银行信贷的低比率也发生在了海得拉巴市区,那里有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他们的借款渠道主要是放债人(52%)、朋友或邻居(24%)、家人(13%),只有5%的借款来自商业银行。在我们所调查的18个国家当中,不到5%的农村穷人会从银行贷款,城镇穷人会这样做的也不到10%。
从非正规渠道借钱所支付的利息一般都很昂贵。在对乌代布尔地区的调查中,对于那些每日生活水平低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平均每月要为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借款支付3.84%的利息(相当于57%的年利息)。即使是美国的信用卡透支(因其代价昂贵而臭名昭著),相比之下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发行美国标准信用卡的银行,其年利率约为20%。那些日消费在99美分到2美元之间的人可以少付一点儿:每月3.13%。这种利率差距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贫穷程度越低的人,对非正规贷款渠道的依赖性就越小,对正式贷款渠道的依赖性就越大,因为正规的渠道更廉价。第二,与不太贫穷的人相比,穷人向非正规渠道支付的利息一般会更高。贷款人所拥有的土地每多出一公顷,他每月要向非正规渠道支付的利息就会下降0.4%。
利率会因国家及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但底线常常是相同的:正常情况下,年利率在40%~200%(或更高)之间,而穷人需支付的利率比富人更高。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在以这一利率水平贷款。上百万人愿意接受的这一贷款利率水平,一定是美国的救助者所乐于赚取的。那么,为什么投资者不拿着一袋子钱去找他们呢?
并非没人尝试过。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政府主办的信贷计划,通常附带利率补贴,是专门针对乡村穷人的。例如,自1977年起,印度每在一个城市设立一家银行分行,该银行就需在没有银行的农村地区额外设立4家分行。此外,银行根据政府指示,要将其40%的贷款提供给一些“重要领域”:小公司、农业合作社等。罗宾·伯吉斯和罗西尼·潘德表示,在因这一政策而额外开设分行的地区,那里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贫穷。
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性的信贷计划并非十分有效,违约率出奇地高(20世纪80年代高达40%)。贷款常常受到政治的驱动,而非出于经济需求(在某些地区,大量贷款都是大选之前向农民提供的,因为人们预计这些地区的选举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且,这些钱最终都会落到当地实力派的手中。伯吉斯和潘德的研究认为,要想通过设立银行分行为穷人增加1卢比的收入,就需要花掉1卢比以上的费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更多分行的地区其实会变得更穷。1992年,在印度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中,政府对于在农村开设分行的要求有所下降。而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趋势,即政府取消了对公共贷款计划的支持。
或许,社会银行实验是一次失败,因为政府不应插手贷款补贴的事务。政客们发现,将贷款用作馈赠非常具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能比无须偿还的贷款更好的了。然而,为什么私人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主呢?这些人愿意每月支付4%的利息,是一家银行普通贷款的几倍,贷款给他们不是更合理吗?通过美国目前的一些网站,我们得知,富国的潜在贷方可以向穷国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弄懂了其他人搞不清楚的问题?
或者,也有可能是,非正式放债人可以做到银行做不到的事情。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贷款给更富有的人成本更少呢?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支付高利率?一个标准的解释就是,他们违约的概率更高。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如果仅仅为了维持运营,一位放债人平均每贷出100卢比,他就要拿回110卢比,即如果不发生违约的话,他可以收取10%的利息。但如果半数的借款人违约了,那么放债人就必须向另一半没违约的借款人至少收取220卢比,一共收取120%的利息。然而,不同于那些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计划,非正式贷款的违约率并不是很高。这种贷款的偿还时间通常会延迟一些,但完全不偿还还是很少见的。一项对巴基斯坦农村放债人的研究发现,放债人所遇到的一般违约率仅为2%。不过他们收取的平均利率高达78%。
问题在于,这种低违约率绝不是自发产生的,这需要贷方付出很大的努力。加强履行贷款合同并不容易,如果借款人挥霍借款,或是遇到了难处,手头没有现金,那么贷方就无钱可收了。在这种情况下,贷方几乎没什么办法收回贷款。因此,借款人即使在自己有钱时也可能会假装没钱,这对贷方来说则会更糟。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制止的话,即使借款人的项目获得了成功,贷方也永远拿不回借出的钱。
为了避免各种故意违约的行为,全世界的贷方保护自身的一个办法就是,收取预付定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也就是所谓的发起人出资,即倡议人出一部分资金。如果借款人违约,贷方可以通过没收附加担保金来实施惩罚。借款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其违约的概率就越小。但这也意味着,借款人所做的担保越大,贷方发放的贷款就会越多。因此,我们看到了那条熟悉的规则(至少在无抵押的投机时期之前),即将可贷款数量与借款人的资金现状挂钩。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会借钱给富人”。
也就是说,更穷的借款人所能得到的贷款更少,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穷人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为什么银行拒绝贷款给他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收回贷款,贷方需要了解很多关于借款人的信息。有些信息是贷方希望在决定贷款之前就了解的,如借款人是否值得信赖、来自哪里、所做生意的性质、收回贷款方面会不会有问题等。贷方或许还想时刻关注着借款人,时常到他家里去看看,确保贷款以承诺的方式使用,并在必要时推动生意向理想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要花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而利率的提升便会抵消这一花费。
此外,很多此类花费并不是以贷款多少来衡量的。即使贷款额非常少,贷方也必须收集某些借款人的基本信息。结果,贷款额越少,作为贷款一部分的监督费用就会越高,而由于这部分费用要由收回的利息来抵消,利率就会变得更高。
更糟糕的是,这会产生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当利率上涨时,借款人有更多理由想办法不偿还贷款。这就意味着,借款人需要受到更为细致的监督,而这又增加了贷款成本。利率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借款人需要更多的监督,如此循环反复。贷方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或者,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贷方或许决定,贷款给穷人并不可行:他们的贷款额太少,不值得一贷。
一旦我们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便一目了然。贷款给穷人的主要限制在于,收集关于他们的信息会产生费用。因此,穷人大多会向熟悉他们的人借钱,比如邻居、老板、生意伙伴或当地的放债人,这恰恰就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虽然,这种对于合同执行的强调似乎有些奇怪,但穷人因此会向那些一旦违约就会真正伤害他们的人借款,因为这些贷方无须花那么多时间去监督(借款人不敢犯错),因而贷款会更便宜一些。20世纪60~70年代,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很多放债人都是喀布尔人——阿富汗的高个子男人,他们肩上挎着一个布袋子,挨家挨户地假装卖水果及坚果,其实大多是以此为掩护,推销他们的贷款业务。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不去开展这些业务呢?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这些阿富汗人以凶悍无情而著称,这种说法来自孟加拉邦学生课本中的一则古老的故事,说的是喀布尔人心肠好,但很暴力,他们会杀掉企图欺骗他们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暴徒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后贷款人”。
在伦敦1999年8月22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可以看到一篇题为“付钱——否则我们就派阉人去见你”的故事,堪称一次对威胁力量的奇特描述。该报道描述了印度的一些收债者利用人们对阉人的传统偏见,让阉人去找那些长期欠款的人收债。因为人们相信,看到阉人的生殖部位会带来厄运,所以一些阉人会根据指示出现在违约者的家里,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就给他们“展示一下”。
收集借款人的信息会产生高额的费用,这就是即使在每个村庄都有几个放债人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并未使利率下跌的原因。假如贷方在监督放债人方面有所投资,那么贷方就会在借款人心中拥有良好的信誉,借款人很难再更换贷方。如果借款人到别处去贷款,新的贷方要重新付出同样的努力,这又要花上大笔费用,会使利率上涨到更高。此外,贷方会对新客户持怀疑态度:解除与以前贷方的关系很费钱,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这样做显然更费钱。在这种情况下,贷方会更为谨慎,而利率也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尽管贷方可以选择,但借款人一般会与自己已经了解的贷方保持关系。而且,放债人会利用这一机会提高利率。
这还可以解释,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穷人。银行职员并不承担必要的监督职责:他们既不住在村里,也不认识那里的人,而且他们的人员流动也很频繁。那些体面的银行是不会与喀布尔人竞争的,银行不会动辄就要打断某人的腿,或是派阉人去找违约者。花旗银行在印度的分行陷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人发现,它们让当地“小流氓”威胁未偿还汽车贷款的人。而且,即使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1988年,印度法律委员会报告说,40%的资产清算(破产借款人)案件都会搁置8年以上。站在贷方的角度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肯定能打赢与违约公司的官司,他们也要等7年才能收回抵押款(在此期间,借款人有充足的机会转移资产)。当然,对于贷方来说,借款人的资产在贷款发生时就已贬值了。
纳奇凯特·摩尔当时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之一,他曾向我们描述,他知道一个让农民偿还农业贷款的绝妙好主意:在支出每笔贷款之前,他会要求农民们提供一张等量钱款的长期支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如果农民拒绝还款,银行就可以叫警察来取支票,因为不兑现支票是一种违法行为。这种方法起初还颇有成效,但后来便逐渐失效了。因为警察意识到,他们需要追踪上百张空头支票,于是他们礼貌地告诉银行,这其实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
即使银行成功收回了贷款,也会产生一定的反效果:银行并不喜欢同“农民自杀”的头条新闻扯上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竞选在即时,政府喜欢勾销一些未偿还贷款。因此,银行干脆就避免贷款给穷人,让放债人来填补这一市场空白。然而,尽管放债人在收回贷款上有优势,但他们要为贷出款项支付比银行更多的钱。这是因为,即使银行支付的存储利息很低(或没有),穷人也愿意将积蓄存在银行,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积蓄押给放债人。而放债人所热衷的“乘数效应”及垄断力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穷人要承受如此高的利率。
因此,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帕德马贾·蕾迪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以更合理的价格贷款给穷人,他们还发现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康复援助委员会及格莱珉银行中出现了并不起眼的小额信贷业务,但这项业务现在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小额信贷触及1.5亿~2亿借款人(主要是女士),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所使用。有时,人们将小额信贷描述得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角色(双头怪物)——兼具赢利使命与社会使命——而且据大家所说,其在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另一方面,2007年春,墨西哥小额信贷公司——康帕多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创造了商业领域的一次(具有争议的)胜利。此次发行为该公司筹集了4.67亿美元,不过人们也注意到,该公司收取的费用为100%以上的利息(尤努斯对此公开表示不满,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为新的高利贷者,但其他小额信贷公司也紧随其后:2010年7月,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公司SK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3.54亿美元的资金)。
由此可以看出尤努斯不喜欢沾染高利贷的原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额信贷是一种基于社会目的的变相放债。正如传统的放债人一样,小额信贷机构依赖的是其紧密监督客户的能力,但其中会涉及借款人碰巧认识客户的情况。典型的小额信贷合同允许一组借款人贷款,他们为彼此的贷款负责,因此必须尽量确保其他人按时还款。有些组织希望,一些借款人前来借款时彼此认识,它们甚至通过每周组织活动让彼此熟识。这些活动有助于客户更好地了解彼此,而且在一位组员暂时遇到困难时,其他人也更愿意伸出援手。
正如放债人一样,对于那些彻底违约的人,小额信贷机构会威胁再也不贷款给他们,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其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对拒不还款的借款人施压。与放债人不同,小额信贷机构的官方政策就是,永远不使用暴力威胁。羞辱的力量确实不小。我们在海得拉巴市见到一个借款人,她正努力偿还几家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她说自己从未拒绝偿还任何欠款,即使她要向自己的孩子借钱还债,或是一天不吃饭:她讨厌信贷职员跑到她家门口,在街坊邻居的面前让她难堪。
小额信贷机构与传统放债人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行事极为谨慎。传统放债人会让他们的借款人选择借款方式及还款方式——有的每周偿还一次,有的不限定还款时期。有些先还利息,钱凑够后再还本金。相反,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一般每周都要偿还一定量的钱,从贷款发出一周之后算起。至少就第一笔贷款来说,每个人收到的钱常常都是等量的。此外,借款人必须要在每周会议上还款,会议召开时间对于每个小组来说都是固定的。这就使得追踪还款情况变得很容易:贷款负责人只需数数手中的钱,看看够不够一个小组该交的钱即可。如果够数的话(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到下一个小组收钱了。因此,一位贷款负责人每天可收回100~200人的欠款,而传统放债人只能在不知何时才能收回钱的情况下坐等。此外,由于交易非常简单,贷款负责人不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培训,因此成本会有所下降。而且,贷款负责人工资的发放依据是过于夸张的奖励合同,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客户并保证每个人都能偿还借款。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管理费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这部分费用因“乘数效应”而增长,导致贷款给穷人变得十分昂贵。这是南亚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的赢利模式,他们贷款给穷人的年利率约为25%,而当地放债人收取的利息一般是这一比率的2~4倍。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利率则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贷款负责人的工资更高了),有时年利率甚至超过100%。而对于穷人来说,这一选择还是比其他选择廉价得多。例如,在巴西的城市里,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月利率约为4%(每年60%),而最容易的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卡还款,月利率在12%~20%之间(每年289%~800%)。然而,违约行为极为少见,至少在不发生政治风波的情况下是如此。2009年,“风险投资组合”(可能会违约的贷款,但并非全部)在南亚低于4%,而在拉丁美洲及非洲国家则不超过7%。因此,小额信贷及其1.5亿~2亿位客户,已经作为最显著的扶贫政策之一得以立足。然而,小额信贷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答案显然取决于你所谓的“效果”是怎样的。对小额信贷较为热情的支持者认为,这意味着改变人们的生活。扶贫协商小组是一个隶属于世界银行的组织,其使命在于推广小额信贷。该组织在其网站“常见问题”板块中报道,“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贫穷家庭可用的金融服务——小额信贷——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例如,普及初级教育、减少儿童死亡率及加强女性健康等)。其核心理念是,使女性手中掌握经济权,女人比男人更关注这些方面。
遗憾的是,与扶贫协商小组的主张相反的是,直到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很少。扶贫协商小组所谓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案例,通常是由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策划出来的。对于小额信贷的很多支持者来说,这似乎已经足够了。在硅谷,我们见到了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及投资家,他也是小额信贷的支持者(他很早就支持SKS)。他告诉我们,为了了解真相,他已经看到了够多的“坊间数据”,但这种数据对于怀疑者们来说根本没用。其他地区的很多政府部门也对此表示担心,小额信贷或许会成为“新型高利贷”。2010年10月,即SKS首次成功发行股票仅两个月之后,安得拉邦政府因57位农民自杀而责怪SKS,据说是由于贷款负责人强制性的收款行为,使这些农民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SKS及斯潘达纳公司的少数贷款负责人被捕,政府因此通过了一项法律,试图阻止他们每周收回贷款的做法。此外,政府还要求还款时要有一位当选官员在场。这表明,借款人不需要着急还款了。到12月初,主要小额信贷机构(SKS、斯潘达纳公司等)的所有贷款负责人仍在坐等,他们的损失在不断上升。SKS的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阿库拉证实,自杀的57位农民并没有违约,因此他们的死不可能是由SKS贷款负责人引起的,但这对于解决问题几乎毫无作用。
小额信贷机构缺乏自我辩护的有力证明,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一直不愿搜集有力证据来证实其影响力。当我们来到小额信贷机构时(始于2002年左右),我们提议与他们合作开展一次评估,而他们对此的通常反应是:“我们为什么要像卖水果的小贩一样做评估呢?”他们的意思是,只要客户提出更多要求,小额信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好处的。而且,由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资金充足,并不依赖于慷慨大方的捐款人,因此评估其优点所在是毫无必要的。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虚伪。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都需要慷慨大方的捐款人,需要员工拥有高涨的工作热情。他们的工作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小额信贷比其他方式更能帮助穷人。有时,这些机构也会享受到政策补贴。在印度,小额信贷具有“优先部门”的资质,它们为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激励方案,以优惠利率给它们贷款,这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高额补贴。
此外,在做长期决定(例如贷款)时,人们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美国媒体报道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人们由于过度使用信用卡而陷入了麻烦。或许,情况并非很多管理人员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贷方的保护。安德拉邦政府认为,借款人在贷款时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有可能还不了款。
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立场,还有部分原因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很多领导其实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帮助穷人。因此,几家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对自身的计划进行评估。我们也参与了斯潘达纳公司在海得拉巴市的计划评估。斯潘达纳公司被认为是业内最赢利的机构之一,也一直是政府在安德拉邦的主要行动对象之一。帕德马贾·蕾迪为斯潘达纳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充满智慧的女人。蕾迪出生于贡土尔市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她哥哥是村里第一个上完中学的人,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哥哥劝说父母让蕾迪上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而蕾迪却想帮助穷人,于是她开始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们在前面讲过,她后来遇见了那个拾破烂的人,开始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当她所在的那家非政府组织拒绝做这项业务时,她创立了斯潘达纳公司。尽管蕾迪在小额信贷业务上付出很多努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在描述小额信贷的潜在益处时非常低调。对于蕾迪来说,小额信贷的获取渠道非常重要,因为它通过一种以前不可能发生的形式,为穷人勾画出了一个未来,而这只是实现他们美好生活的第一步。无论他们是否购买机器、工具,或是给家里买台电视机,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穷人会在必要时储蓄、争取机会并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不再混日子,而是朝着他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迈进。
或许,由于蕾迪一直非常谨慎,从不去做过分的承诺,因此她同意与我们合作评估斯潘达纳公司的计划。该评估是基于斯潘达纳公司在海得拉巴市某些地区的业务拓展展开的。在104个社区之中,我们随机选择了52个社区让斯潘达纳公司进驻,其余的社区作为一个对照组。
我们对两组社区家庭进行了比较,在斯潘达纳公司开始贷款的15~18个月左右,小额信贷开始发挥明显的作用。斯潘达纳公司社区的人们更可能会经营自己的生意,购买大量的耐用品,如自行车、冰箱或电视。至于那些没有经营生意的家庭,他们在这些社区的消费更多,而经营生意的家庭实际上消费更少,因为他们要节衣缩食,从而充分利用新的机会。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显示,出现了有些评论员所担心的盲目消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有些家庭认为有点儿“浪费”的支出(如茶叶、零食)上,他们花的钱更少了。或许这就像蕾迪所预计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有了更好的了解。
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彻底的转变。女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如此。例如,在整个家庭的消费上,她们手中并没有更多的控制权。在关于教育、健康及孩子上私立学校的问题上,我们也没看到任何变化。即使小额信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人们开始做起了新的生意,这种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在15个月间,开始做新生意的家庭从5%左右上升至7%以上——这一比率不算低,但也算不上一场革命。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这些结果感到很高兴: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了。对此,我们需要展开更多研究,以证明其合理性。而且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趋势未来的发展态势。但至今为止,一切都发展顺利。在我们看来,小额信贷已经赢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成为抗击贫穷的关键手段之一。
有意思的是,媒体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引入了一些负面的发现,证明小额信贷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而且,尽管一些小额信贷机构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主要是蕾迪,她说这正是她所预料的情况,并投资展开第二轮关于长期影响的研究),一些国际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决定发起反攻。
就在一项研究公之于众后不久,全球最大的6家小额信贷机构——“六巨头”(尤尼特斯公司、美国行动国际公司、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格莱珉基金会、国际机遇及妇女世界银行)——派出代表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一次会议。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同行的还有同事伊巴·达哈里瓦,我们认为,会上一定会对研究结果进行一些讨论。然而,这6家公司只是想了解,其他一些随机的影响力调查何时出结果,以便他们组建一个特别小组,做好应对问题的准备(他们显然已经相信,所有的研究都是负面的)。几周之后,特别小组首次提交了关于损失控制的报告。小额信贷机构回应了来自两项研究(一项是我们的研究,另一项是迪恩·卡尔兰和乔纳森·辛曼的研究)的证据,还有6则借款人的成功故事。此后,《西雅图时报》刊登了尤尼特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里吉特·赫尔姆斯的专栏文章。该文章简洁地指出,“这些研究给人留下了不准确的印象,即扩大基本金融服务获取渠道没有任何好处”。这读起来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证据与此恰恰相反,小额信贷是一种有用的金融产品。然而,这显然不够。很多主要的小额信贷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夸大其词,它们显然已相信这种负面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股票和重组,并承认小额信贷只是抗击贫穷可能的方法之一。
幸运的是,这似乎并不是该行业其他机构的选择。2010年秋,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提出了类似的结果,所有与会人士一致同意,小额信贷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有其优点和缺点。下面我们将看看,小额信贷机构可以为其客户提供哪些更多的服务。
为什么小额信贷机构以前没有提供更多的服务?既然很多家庭可以通过支付利率来获取资金,为什么他们没有用这笔资金做新的生意呢?部分原因在于,即使能够借到钱(这一情况的成因是第九章关于企业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很多穷人也不愿或不能开始做生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三家或更多的小额信贷机构为海得拉巴市的贫民提供贷款,只有约1/4的家庭会向其借款,而半数的家庭会以更高的利率向放债人借款,他们几乎不会因小额信贷的出现而改变主意。我们不能完全解释小额信贷为什么不受欢迎,或许与之有关系的正是小额信贷的严格规定及其施加于客户的时间成本。
标准小额信贷模式的严格及规范意味着,一方面,由于组员需要对彼此负责,因此那些不喜欢掺和别人生意的女士便不愿参加;另一方面,组员或许不愿组里吸收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人,因此他们会歧视新人。组员要承担共同责任这一规定会排除那些想要冒险的人:作为一个组员,你总会想让其他组员尽量安全地操作。
贷款支出一周后开始每周还款,这对于那些急需用钱的人来说并不现实,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还款。小额信贷机构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有时他们将紧急的医疗支出排除在外,但这只是人们需要紧急贷款的众多原因之一。例如,你的儿子突然得到一次学习机会,这对他的事业有很大帮助,但学习费用是100万卢比(购买力平价179美元),需要下周日付款。或许,你会向当地放债人借钱来支付学费,然后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还清贷款。然而,小额信贷不会为你提供这种灵活的选择。
同样的要求还会阻碍人们选择一些赚钱慢的项目,因为他们每周都需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按期还款。罗西尼·潘德和埃里克·菲尔德劝说印度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位于加尔各答市的村庄福利协会,允许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在得到贷款两个月之后开始还款,而不是一周之后。当对稍后还款的客户与遵循标准还款期限的客户进行对比时,他们发现,前者更可能会做更大更冒险的生意,比如买一台缝纫机,而不是仅仅倒卖莎丽服。这意味着,他们将来或许能赚到更多的钱。然而,尽管客户满意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这家小额信贷机构依旧决定重新采用传统模式,因为新贷款小组的违约率(虽然非常低)比原计划高出8% 。
总而言之,小额信贷机构对于零违约率的关注确定了它们对其潜在借款人的严格要求。小额信贷精神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企业家精神常常意味着冒险,而且无疑还有偶尔的亏损。例如,在备受争论的美国模式中,破产情况时有发生(或者至少曾经是这样),这并不会留下污点(恰恰与欧洲模式相反),这与企业家文化的活力有着很大关系。相反,小额信贷的规则不容忍任何失败。
小额信贷机构坚持零违约率是否正确?从社会及商业角度来看,这些机构能否做得更好?如制定一些为违约留有一丝余地的规则。小额信贷机构的大多数领导都坚信,情况并非如此,对违约放松限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不过,他们或许是对的。毕竟,他们的经营环境使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如果客户拒不还款,就意味着他们将像银行一样,不得不依赖烦琐的诉讼程序来催款。从很多层面来看,他们的成功源于将还款设定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契约,由整个社区来确保还款,而小额信贷机构会继续提供贷款服务。这种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小额信贷机构放弃了承担共同责任的正式要求。的确,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客户们定期会面,无论他们是否承担共同责任,他们在还款方面无任何差别(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客户不是每周会面,而是每月会面,那么该小组的社会关系就会建立得较慢,其违约率最终也会上升)。
然而,基于共同责任的社会平衡及不断发展的关系似乎并不稳定。如果我还款的理由有二,一是所有人都还了款,二是我将来还会得到新的贷款,那么与我是否还款紧密相连的是,我对别人正在做什么以及这一组织的将来是怎样看的。的确,如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违约,那么我会认为该机构就要破产,并因此不再从那里贷款。结果,当信念有所改变时,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了。
这就是斯潘达纳公司发生的情况,该公司位于安得拉邦的克里斯那地区,这里是印度小额信贷运动的中心地带。该地区的一些官僚及政客们热衷于推广自己的小额信贷品牌,并且决定摆脱竞争。突然,在2005年的某一天,一家当地报纸(在某种意义上是伪报纸)登满了关于蕾迪的故事。有些故事说她逃到了美国,另一些故事说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其中的隐含意义是,斯潘达纳公司已经没有未来了,因此偿还该公司的贷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的一张“报纸”称,蕾迪自己甚至建议他们违约,因为她已经赚够了钱,并且打算退出了。
这种彻底毁掉一家机构的方式,确实是改变人们信念的一种高超手段:让人们相信一家小额信贷机构没有未来,这是确保其真正没有未来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这样一来,使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的做法就是违约。蕾迪几乎要发疯了(虽然她对于自己逃到美国躲债的想法感到可笑——毕竟,借款人手里有她的钱,而不是恰恰相反),但她决定发起反击。她开车跑遍了国内,出现在每个小城镇及大村庄的会议上。她说:“我还在这里,没有去任何地方。”
这一特殊的危机因此而扭转,但几个月之后,即在2006年3月爆发的一则新“丑闻”中,该公司的弱势再次被揭露。这一次,斯潘达纳公司及Share公司(其竞争者之一)被控与大量农民自杀有关。根据媒体一系列新的报道,贷款负责人逼迫客户过度借款,然后对其施加不公正的还款压力。这两家小额信贷机构明确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克里斯那地区行政长官判决,任何人向斯潘达纳公司或Share公司还款皆是“非法”的。几天之内,克里斯那地区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停止了还款。在危机期间,斯潘达纳公司在克里斯那地区的未偿还本金约为5.9亿卢比(购买力平价为3 450万美元),占斯潘达纳公司2006年在印度15%的总贷款额。
各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纷纷上诉,这一判决结果很快被废除了,但损失却已然铸成。人们还款是因为别人都在还款,而一旦人们停止还款,便很难再重新开始。一年之后,70%的未偿还本金仍未到账。自那时起,斯潘达纳公司的贷款负责人便开始前往每一个受影响的村庄,向他们的客户提供新贷款,但前提是,他们要偿还以前的欠款(无额外利息)。这些提议在某些村庄的确有效,他们目前只需追回一半的未偿还本金,但让别人也照做的压力显然很大。在有些村庄,每个人都会还款。而在另一些村庄,每个人都拒绝还款,甚至包括那些只需几次还款就能得到新贷款的人。即使那些只需一次还款就能得到新贷款的人只还款约150卢比就能得到8 000卢比,他们可以用来还款或是拿在手里,然后再次违约,也还有1/4贷款未偿还。在这些违约者所在的小组中,一般都没有人还款。
尽管没有明确的政治干预,克里斯那还款危机仍在重演。2008—2009年,卡纳塔克邦和奥里萨邦分别爆发了KAS(另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破产的事件。由于KAS失去了流动资金的获取渠道,无法发放新的贷款,所以每个人都停止了还款。2010年秋天安德拉邦危机几乎是2006年危机的重演,其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政客们再一次将农民自杀当作攻击小额信贷机构的一种根据,而且在政府介入之后还款便完全停止。这将几家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SKS、斯潘达纳公司及Share公司)推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表明,小额信贷机构注重信念的掌控或许是正确的,因此他们有理由更加注重还款规则。即使是为了鼓励人们承担必要的风险而允许违约,也可能会导致社会契约的瓦解,而这份契约正是使他们保持高还款率并享受较低利率的保障。
对还款规则的必要关注表明,对于想要扩大企业规模的企业家来说,小额信贷并非集资的最佳方式。就硅谷或其他地方的成功企业家来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会遭遇失败。我们看到,对于将大笔资金给予可能会失败的人,小额信贷模式的设计并不适用。这种危机并非出于偶然,也并非是由小额信贷的某种缺陷造成的。这是某些规则实施的必要附属品,这些规则允许小额信贷以低利率贷款给大量穷人。
此外,小额信贷甚至不是一种发现企业家的有效方式,包括那些将进一步创建大企业的企业家。小额信贷鼓励其客户进行安全交易,因此并不能发现敢于冒险的生意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每一家小额信贷机构都会在其网站上夸耀,描述那些小商店怎样发展成了连锁店,但这样的实例太少了。在第一个三年周期,斯潘达纳公司发放的平均贷款仅从7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320美元)增加至1万卢比(购买力平价460美元),而且几乎没有超过15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686美元)的贷款。在运营了30多年之后,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仍然很少。
小额信贷不适用于那些借贷金额较大的人,然而,这或许也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看到,相对于更富有的人来说,贫穷的借款人所受到的贷款限制可能更严格。或许这是一种自然的渐进过程——从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贷款作为起步,将生意做大,然后转向银行。
遗憾的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经营状况稳定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贷款。这类公司常常要冒这样一种风险,即对于传统放债人及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它们的规模太大了;而对于银行来说,它们的规模又太小了。苗磊是中国杭州一位很有前途的商人,他接受过工程师的培训。2010年夏,他开始做起在当地各家公司安装计算机系统的生意。当时的问题是,他首先需要购买硬件和软件,而他只有在安装完系统之后才能拿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贷款给他。有一次,他有机会竞标一份利润空间很大的合同,但他手头上的现金显然不够。然而,这一次的诱惑力非常大,他不顾一切地参加了竞标。他还记得自己在公司中标后的那些日子,为了筹钱而四处奔走,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一旦发生合同违约,他的事业就将终结。在绝望中,他决定玩一次更大的赌博。当时有一家国有企业的合同在竞标,苗磊知道,如果他中了标,他就会得到一笔预付款,用这笔钱他就可以完成第一份合同。然后,他或许可以用第一份合同赚的钱完成第二份合同。他决定全力以赴地竞标——他甚至愿意为了中标而花点儿钱。他还记得那个晚上,他正在等待中标结果。那天,他很早就让员工下班了,一连几个小时,他一直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他中标了,一切都如愿以偿。资金注入,随之而来的是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一旦他的收入超过2 000万元,银行家就会找上门来)。当我们见到苗磊时,他正经营着4家公司。
苗磊拥有很好的学历背景,还具备一种合理的经商模式,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那拉彦·摩尔西和南丹·奈尔肯尼等人尽管拥有印度著名技术学院的学历,却得不到一份贷款来创建印孚瑟斯公司,因为银行家提出,银行看不到贷款所需的抵押资产清单。今天,印孚瑟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我们可以想象,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们不能在适当的时间得到适当的资金。
即使有些生意可以开始、维持下去并发展到一定规模,但在获取资金方面,它们似乎也要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印度南部城镇蒂鲁布尔是印度最大的T恤产地(印度70%的针织服装都产自这里)。在该地区经营的这些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全世界的买主都会到这里下笔大订单。因此,该城镇吸引了全印度那些最有才华的纺织企业家,还有很多当地的企业家,即富裕农民家庭的子孙。毫无疑问,外来者都是这一行业的专家,他们所经营的公司比当地企业家创建的公司效率更高。无论是任何资金水平,这些公司的产出量及出口量都更多。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地企业家创建公司的启动资金是那些外来者创建公司的三倍多。当地富有的企业家们不会借钱给那些外来者——这一行业的专家,即使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也会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为什么银行没有介入、帮助那些外来者开创更大的生意?答案是,即使是这样的大公司(一位外来者名下的公司平均有290万卢比的股本,购买力平价34.7万美元),也会遇到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问题。当地企业家们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社区,而且他们并不确定外来者是否会还款。
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利用规定使银行贷款给较大的企业。印度有一个“优先部门”规定,银行要向优先部门提供该部门贷款总额的40%,这些部门包括农业部门、小额信贷机构、中小型企业,也包括一些大公司(最大的公司比印度95%的公司还要大)。而且,公司显然能够高效投资部分资金。1998年,优先部门有所扩大,囊括了一些较大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进入优先部门领域,用额外的贷款进行投资,赚了一大笔钱。贷款每增长10%,还款之后的赢利就会增加9%。这是一个很高的回报率。然而,今天的趋势是消除这种强制贷款,部分原因在于,银行抱怨,贷款给这些公司代价很高、风险很大。
有些人试图找出有潜力的新生意,然后提供投资。中国商人苗磊就是如此,或许这来源于他自己的经验。他从有潜力的新兴公司买入普通股,但我们并未看到中小企业类似的小额信贷变革;尚未有人搞清楚,怎样在大范围内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商业环境的改变(如法庭功能的改进)或许能对此有所助益。在印度,法庭诉讼程序的加快促进了还款行动的进行,也带来了更多的贷款及更低的利率。然而,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解决。引入还债法庭增加了给予大公司的贷款,减少了给予小公司的贷款。这似乎是因为,银行官员发现,贷款给大公司赢利更高,因为银行能够确保自身收回贷款。
最终,我们将这一问题归因于银行的结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银行是大型机构,很难鼓励自己的员工对公司进行监督、对项目进行跟踪,并做出赢利性投资。例如,如果银行决定因违约而惩罚贷款负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必须这样做),贷款负责人便会寻找绝对安全的项目,而无名小公司的项目当然不在其列。未来的苗磊或那拉彦·摩尔西或许就得不到贷款。
小额信贷运动表明,尽管困难重重,贷款给穷人还是可能的。尽管有人会争辩,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穷人的生活,但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发展成了其目前的规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很少有项目会覆盖这么多的穷人。然而,该计划的结构是成功贷款给穷人的根本,我们也不指望其成为较大企业创建及筹资的踏脚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来说,下一个大挑战就是找到贷款给中等企业的方式。
几 乎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市中心驱车前往较为贫穷的乡村地区,令人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那些未建成的房屋。有的房子四面有墙但没有屋顶,有的房子有房顶却没有窗户,未建成的房屋可能只有一两面墙,房梁伸出了屋顶,墙上有画过的痕迹却不完整。在那里,我们看不到水泥搅拌机或泥瓦匠,大多数这样的房子只建了几个月。然而,在摩洛哥丹吉尔市一些较新的社区里,比较显眼的都是一些建好的、刚刚被粉刷过的房屋。
如果你问房主为什么保留未建成的房屋,他们的回答通常很简单:这是一种省钱方式。这种情况听上去很熟悉。当阿比吉特的祖父多赚了一点儿钱时,他就会多建一间房子。一次建一间房子,他家住的房子就是这样建成的。比较穷的人建不起一整间房子。阿比吉特家过去有过一个司机,他偶尔会请一天假,买些水泥、沙土和砖,然后盖房子。他的房子已经建了很多年了,一次只垒100块砖。
乍看上去,未建成的房子似乎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省钱方式。人们不能生活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只建了一半的房子下雨天会坍塌;如果在房屋建成之前急需用钱,那么房子就要在这种状态下出售,未建成房子的价值比最初买砖的成本或许还要低。出于这些原因,节省现金(如存到银行)似乎更实用些。等钱积攒到了一定的数目,他们就会至少建一整间带屋顶的房子,一次到位。
如果穷人仍然一砖一瓦地节省,那么原因一定是,他们没有省钱的更好方式。银行是还没找到一种吸纳穷人储蓄的方式,还是将会发生一场“小额储蓄革命”?或者是我们还未想到的一种原因,导致未建成的房屋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我们是否应为人们超凡的耐心而感到震撼——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常常低于99美分,而为了建成自己的房屋,他们很多年都享受不到一点点生活乐趣。或者我们应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砖一瓦地建房是拥有一所房屋的唯一方式,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存更多的钱,将房屋建得更快一些呢?
鉴于穷人几乎没有获取贷款的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他们不是应该尽量储蓄更多的钱吗?储蓄可以使他们在遭遇灾年或疾病时有所保障,还可以使他们做点儿自己的生意。
在这一点上,一个常见的反应就是,“穷人怎么存钱?他们没有钱啊?”但这仅仅是一个表面意义:穷人应该存钱,因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都有一个现在和一个将来。他们今天只有一点儿钱,除非他们晚上能捡个装满现金的钱包,否则明天可能仍然只有一点儿钱。的确,他们应比富人有更多存钱的理由。如果他们存了一定的钱,将来就能躲过一场灾难。例如,通过这样一种金融缓冲,印度乌代布尔地区的贫穷家庭在钱花光时就不至于减餐,他们曾说减餐会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快。同样,在肯尼亚,如果一个市场小贩患上了疟疾,那么他的家庭为了给他买药,就要拿出一部分运营资金,但小贩病好后却很难继续做生意,因为他几乎无货可卖。如果他们以前存了一些买药的钱,不就能避免这一切了吗?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这本来就是穷人的状态——耐心不够、不会未雨绸缪。因此,他们相信,避免穷人陷入懒惰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如果他们偏离正轨,就以极度贫苦的生活来吓唬他们。所以,他们有噩梦般的救济院(穷人住的地方),还有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欠债者监狱。有观点认为,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天生就目光短浅,所以才会贫穷。这种观点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续多年。今天,在小额信贷机构的批评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相同的观点,他们指责小额信贷机构助长了穷人的浪费之风。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
最近,小额信贷热衷者和其他一些人发起了一项运动,即认识每一个贫穷男人及女人内心的资本主义萌芽。这项运动使我们放弃了对于穷人的这种观点,即穷人并非无忧无虑的,也不是完全无能的。
我们在第六章关于风险及保险的部分提到,穷人实际上始终在担心未来(特别是潜在的灾难),他们会巧妙利用所有廉价的或昂贵的预防措施,降低他们会遇到的风险。穷人在管理自己的经济时,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聪明才智。他们很少在正式的储蓄机构开户。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在中等发达国家(例如印尼),7%的农村穷人及8%的城市穷人都有正式储蓄账户。在巴西、巴拿马及秘鲁,这一比率低于1%。然而,这些国家的人们也会存钱。斯图尔特·卢瑟福是“安全储蓄”(SafeSave)的创始人,这是孟加拉国一家专门帮助穷人储蓄的小额信贷机构。卢瑟福在两本书中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即《穷人和他们的钱》 (The Poor and Their Money )和《穷人文件夹》(Portfolios of the Poor )。作为这两本书的背景,孟加拉国、印度及南非250个贫穷家庭向调查研究人员描述了其每一笔经济交易,研究人员会连续一年对这些家庭进行走访,每两周一次。他们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穷人找到了很多巧妙的储蓄方法。他们同其他储蓄者们结成“储蓄俱乐部”,其中每一位成员都要确保其他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储蓄目标。自助小组在印度的某些地区非常流行,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很常见。它利用全体成员积攒的储蓄,向其组员提供贷款。在非洲,最流行的方式是轮转基金——在说英语的非洲国家,更普遍地被称为“旋转木马”,而在讲法语的国家则被称为“唐提式保险”。轮转基金的成员会定期见面,每次见面时,所有人都将相同数量的钱存入一个公用钱罐。基于轮换的方式,每一次会有一个成员拿走整个钱罐。其他的储蓄安排包括,雇用收款员取走他们的存款并将其存入银行,将储蓄存给当地放债人并留下“看钱人”(免费或收取一点点儿费用、负责照看一小笔钱的熟人)。还有我们看到的,慢节奏地建造一所房屋。美国也有类似的机构,大多是在新移民的社区里。
珍妮弗·奥马是肯尼亚西部布玛拉小镇的一个市场小贩,她充分展示了其聪明才智。奥马贩卖玉米、高粱和豆子。在我们整个谈话期间,她熟练地挑选豆子,将白豆子放到一边,红豆子放到另一边。我们见到她时,她同时加入的轮转基金不少于6家,这些机构只是规模及见面频率有所不同。在其中一家,她每月存入1 000肯尼亚先令(购买力平价17.5美元),而在另一家,她每隔两个月会存入580肯尼亚先令(其中500先令存入钱罐,50先令用于支付茶水、甜点——这是会议场合的必要支出,另外30先令用于福利基金)。在另一家,她的存款为每月500肯尼亚先令,再加上200先令的额外储蓄。然后,还有一个每周轮转基金(每周150先令),有每周见面三次(50先令)的,每天都见面的(20先令)。奥马说,每个轮转基金都有一个独立而具体的目标。到小一点儿的机构存钱是为了她的房租(在她建房之前),而到大一点儿的机构存钱则为了一些长远的计划(例如修缮房屋或交学费)。奥马认为,与传统的储蓄账户相比,轮转基金有很多好处:不收取费用,可以进行小额储蓄,而且在每周存相同数量的钱之后,她会更快地取走钱罐。此外,轮转基金还是一个寻求建议的好地方。
然而,她的储蓄文件夹中并不止6家轮转基金。2009年5月初(在我们见到她之前两个月左右),她从一家轮转基金中取走一笔贷款,用于购买价值6 000肯尼亚先令(购买力平价105美元)的玉米。她还是村储蓄银行的成员,在那里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不过目前账户里没多少钱。账户里的钱被她用于在村银行购买了价值12 000先令(购买力平价210美元)的股票。连同她手中已有的一些股票(每张股票允许借款人从村银行借款4先令),她可以借到7万先令(购买力平价1 222美元),为自己建一栋房子。她还存了一点儿私房钱,分别藏在家里的不同位置,用于应对一些小危机,如健康需要等。不过,她还指出,有时健康储蓄也会用于招待客人。最终,很多人都欠了她的钱,包括她客户的1 200先令,还有村银行共同责任组以前一个成员欠她的4 000先令。这个成员已经违约了,他还欠银行6万先令(购买力平价1 050美元),导致该组全体成员都要为他垫资,而他目前仍在慢慢地还钱。
作为一位嫁给了一个农民的市场小贩,珍妮弗·奥马每天的生活费可能低于2美元。然而,她有一组精确协调的金融工具,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经济才智。
然而,穷人的所有储蓄才智可能仅仅展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无法拥有更常规、更简单的选择。银行不喜欢操作小额账户,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行政成本过高。吸收存款机构受到严格的监管,理由很充分,政府担心逃债者会卷走人们的存款——但这意味着,相对于银行希望从这类小账户中所赚的钱,操作每一个账户都需要银行职员做一些文案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觉得枯燥乏味的。珍妮弗·奥马向我们解释道,在村银行开储蓄账户并不是小额存款的好方法,因为取款手续费太高了。取款低于500先令收取手续费30先令,取款在500至1 000先令之间收取50先令手续费,而更大数目的取款将收取100先令的手续费。由于这一高昂的管理费,即使可以在银行开户,大多数穷人或许也不想这样去做。
由于缺少获取适当银行账户的渠道,穷人会采取复杂而又利息高昂的存款策略。这一事实或许还意味着,如果他们有了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会尽量存更少的钱。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帕斯卡利娜·迪帕和乔纳森·罗宾逊找到当地一家银行,支付了开户费,他们代表的是随机选择的一些小业主(自行车出租司机、市场小贩、木匠等)。这家银行在各个主要市场都设有办公点,小业主们都在这一地区做生意。这种账户不支付任何利息,反而在每次取款时还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几乎没有人使用这种账户,但约2/3的女性至少存过一次钱。而且,与没得到这一账户的女性相比,有账户的女性会存更多的钱,并会为自己的生意投入更多,在生病时取出运营资金的概率也更小。6个月之后,她们每天为自己及家里所购买的食品平均增加了10%。
尽管穷人能找到一些巧妙的存钱方法,但这些结果表明,如果银行开户费用更低,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充裕一些。实际上,肯尼亚每个账户的开户费用为450先令,而在任何至少用过一次的账户存款,则平均需要5 000先令。这就意味着,如果迪帕和罗宾逊没有为那些贫穷的客户支付开户费,他们就要为拥有一个账户而支付近10%的“税费”,这还不包括取款的手续费。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加上穷人去银行的成本,因为银行一般都在距离他们住所很远的城镇中心。在储蓄账户对穷人放宽经济政策之前,银行操作小额存款的成本必须有所下降。
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盛行的自助小组推行了一种减少成本的方式,并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如果组员共用存款并协调他们的存取款,账户中的存款总量就会变大,那么银行将会很愿意接手。此外,技术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肯尼亚,M-PESA手机支付系统允许用户们将有存款的账户连接到他们的手机,然后用手机向其他人的账户汇款,进行支付操作。例如,像珍妮弗·奥马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当地任何一家是M-PESA关系户的杂货店存入现金。奥马因此会得到M-PESA账户,给在缅甸拉穆的表弟发个信息,他的表弟就可以凭借这一信息到当地的一家M-PESA关系户取款。一旦表弟将款取出,奥马M-PESA账户中的钱就会相应减少。一旦M-PESA账户与银行连接,人们就可以通过当地的M-PESA关系户进行汇款、转账,无须长途跋涉前往银行办理。
当然,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消除对于银行账户管理的需求。问题的一部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根据现有规定,只有银行的高薪职员才有权处理客户的存款,这或许没有必要。相反,银行可以利用当地店主收取存款,只要店主发给存款人一张票据,存款人就可凭该票据到银行取款,这样存款人就可以受到保护。接下来,确保店主不会卷走存款人的钱就是银行的责任。如果银行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很多银行都愿意——那么管理者还在乎什么呢?这一认识近年来经过了系统的过滤,很多国家都通过了新的法律,允许这种形式的存款(例如,在印度,这种形式被称为“银行代理法案”)。最终,这种存款方式可能会改变整个存款业务体系。
目前,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国际运动,旨在拓宽穷人获取储蓄账户的渠道。小额储蓄将成为下一场革命。然而,缺乏正式的储蓄账户渠道是唯一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应专注于将储蓄变得简单而安全?迪帕和罗宾逊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首先,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男人都不使用他们的(免费)账户,很多女人也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这种账户。40%的女性没有在这个账户中存过钱,很多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肯尼亚的一项研究中,只有25%的夫妇在免费得到的三个账户(夫妇俩一人一个,还有一个共同账户)中存过钱。而对于那些免费得到一张银行卡的人,这一使用率上升至31%,因为用银行卡取钱更简单、更便宜。储蓄账户显然帮助了一些人,但缺少这种账户并非是阻碍穷人存钱的唯一因素。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有大量的存钱机会,但他们并未加以利用:如陈耐市的水果小贩,她们每天早晨以每天4.69%的利率借款约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假设这些小贩决定连续三天少喝两杯茶,那么她们每天能节省5卢比,这样就可以少借一些钱。第一天她们可以少借5卢比,也就是说,到第二天快要过去时,她们可以少还款5.23卢比(少借的5卢比加上0.23卢比的利息);第二天继续少喝两杯茶,她们就可以少借款10.47卢比;以这一逻辑来看,到了第四天,她们已经节省下来15.71卢比,可以用这笔钱来购进水果而无须再借款。然后,她们可以照常喝茶,但继续将三天来省下的15.71卢比用作周转资金(也就是说借款更少)。这一数目将逐渐增加,9天之后,她们就可以完全还清欠款。她们每天都可以省下40卢比,这相当于半天的工资,一切都来自6杯茶的价值。
关键在于,这些小贩似乎就坐在随处可见的摇钱树旁边,她们为什么不再用力摇一摇呢?
了解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安德烈·施莱费尔或许最能说明一种理论(他创造并推广了“噪音交易者”一词,用来描述天真的股票交易者的行为,他们受到那些无情的股票老手的剥削),即很多人有时会做傻事。他最近刚刚从肯尼亚回来,与我们分享了他在那里观察到的现象:一组修女耕种的田地非常肥沃,而她们邻居所耕种的田地却不怎么好。修女们使用了化肥和杂交种子。施莱费尔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标志着农民们不够耐心(修女的职业或许使她们更有耐心,因为她们相信来世的好处)?
他的研究触及了我们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谜团。在几年来所开展的调查中,迈克尔·克雷默、乔纳森·罗宾逊和埃斯特发现,肯尼亚西部布西亚地区只有约40%的农民用过化肥,而只有25%的农民每年都用化肥。他们做过这一实验,即向随机一组农民提供免费化肥,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用一小部分,然后与那些没使用过化肥的地对比。结果表明,使用化肥的土地年均收益多出70%:每支付1美元购买化肥,普通农民就可以额外收获价值1.7美元的玉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多用点儿化肥呢?或许农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化肥。或者,他们低估了化肥所产生的回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至少那些免费得到化肥及高回报的农民会非常热衷于在下一个耕种季节里使用化肥。实际上,克雷默、罗宾逊和埃斯特研究发现,在一个季节里免费得到化肥的农民,他们在下一个季节使用化肥的概率平均增加了10%。但这仍然意味着,大部分农民都不使用化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化肥不感兴趣:大多数农民都表示自己相信化肥的效果,而且起初还说过他们肯定会使用化肥。
我们问一些农民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使用化肥,大多数人都回答说,在耕种季节到来时,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买化肥。令人惊讶的是,化肥可以少量购买,因此即使对于只有少量存款的农民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不难抓住的投资机会。这表明,问题在于,在丰收至耕种期间,农民们甚至很难存下一点点钱。为家里存钱很难,因为他们总会有要用钱的问题出现(有人生病、有人需要买衣服、有客人需要招待),人们很难对这些问题说“不”。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名叫威克利夫·欧迪诺的农民,他找到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在收割之后,他总是针对是否买化肥做出决定。如果收成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人的口粮,他就会立即卖掉余下的农作物,用这笔钱购买杂交种子;如果还有多余的钱,他就会用来买化肥。欧迪诺会将种子和化肥储存到下一个耕种季节。他向我们解释说,他总是提前购买化肥,因为他知道,钱放在家里根本存不住。他说,只要钱一放在家里,就总会有事情发生,钱就会被花掉。
我们问欧迪诺,如果他买了化肥而家里有人生病了,他是否会以亏本价卖掉化肥?他的回答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卖掉化肥。相反,他会重新评估事态的紧急程度,如果实在需要花钱而手中没钱的话,他会杀一只鸡或是兼职做自行车出租司机(他在农闲时也会做这样的兼职)来赚钱。欧迪诺认为,努力找到一种可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花掉家里的钱,这样做更有效。
因此,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克雷默、罗宾逊和埃斯特设计了存款与化肥行动计划(Savings and Fertilizer Initiative,SAFI)。在收割过后——当农民们手中有钱时——他们得到一次购买一张优惠券的机会,他们可以凭券在耕种季节使用化肥。ICS(该地区一个非政府组织)执行了这一计划。化肥以市场价格出售,但ICS人员上门向农民们出售优惠券,而且可以在农民需要用化肥时送货上门。该计划将使用化肥的农民人数至少提高了50%。确切地说,这一计划的效果超过了给化肥降价50%的效果。正如克雷默所预计的那样,只要在正确的时间提供上门服务,农民们就会很愿意购买化肥。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农民为什么不自己提前买化肥。大部分购买优惠券的农民都要求立即送货,他们会将化肥储存起来以备后用。换句话说,正如欧迪诺所说,一旦他们有了化肥就不会再卖掉。但是,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化肥,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化肥店在收割季节之后并不一定总有货,只是在更晚的时候或播种前才有货。对于欧迪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做兼职自行车出租司机时,可以常常到城里看看化肥是否有货,而且可以在任何一家有货的店里买到化肥。而对于住得离城里较远的人来说,他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一小小的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储蓄及生产效率,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个小障碍。
印度水果小贩及肯尼亚农民的经历表明,有些人即使能够获取良好的存钱机会,也存不住钱。这说明,存钱的障碍并非全都来自外部压力,部分原因还在于人类的心理因素。
我们在第三章关于预防性医疗的部分讨论过,人脑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在和未来进行处理。本质上,我们似乎可以预见自己将来的行动,但这常常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不一致。这种“时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花钱的同时,也在计划着将来省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有耐心。
“时间矛盾”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买下我们今天想要的东西(酒、糖或脂肪类食品,小饰品等),但计划着明天将钱花在一些更合理的地方(学费、蚊帐、修缮屋顶等)。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着会在将来购买的东西,并不总是我们今天已经买下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讲,酒对于很多人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会使我们立即产生反应,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预想的快感。相反,电视机或许不是一种有诱惑力的产品,但很多穷人都会为了买一台电视机,计划并存上几个月或几年的钱。
一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及神经病学家共同研究确定,这种决策上的分裂有其生理基础。他们让参与者们选择各种各样的奖品,通过使用有时间期限的礼品卡,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获取不同的奖品。因此,每位参与者都要做出很多决定。例如,现在收到20美元或两周后收到30美元(现在与将来);两周后收到20美元或4周后收到30美元(将来与稍远的将来);4周后收到20美元或6周后收到30美元(稍远的将来与更远的将来)。关键在于,参与者在做决定时会受到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他们脑部区域的运动将得到呈现。他们发现,只有在对今天与将来的奖品做比较时,脑部的边缘系统(应对即刻奖品的思维)才会产生运动。对于其他决定,无论做出选择的时间是怎样的,侧面的前额皮层(大脑更具计算能力的部分)在应对所有问题时,都会产生类似的紧张程度。
大脑的这种工作会摧毁很多良好的意愿。的确,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从新年决定到未实现的体操馆会员身份。然而,很多人(如欧迪诺)似乎完全意识到了这种不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谈到了以化肥的方式将钱冻结。他们似乎还确信,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紧急事件”,其实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产品。
在海得拉巴市,我们明确地问那些贫民窟居民,有些产品是否是他们愿意舍弃的。他们很快想到了茶、零食及烟酒。的确,从他们的答案及我们搜集的数据来看,他们的预算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这些东西上。
鉴于这种自我意识,穷人的很多存款方式似乎都是为了保障钱的安全(既要防别人也要防自己)。例如,如果你想实现一个目标(买一头奶牛、一台电冰箱或是让房子有屋顶),加入一家足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轮转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一旦加入,就要每周或每月存入一定数量的钱,而当你拿到钱罐时,你就有足够的钱去买你一直想买的东西,马上去买,以防钱从你手中悄悄溜走。要确保你的存款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目标,一砖一瓦地建房或许也是一种办法。
的确,如果缺乏自我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雇用某人来强迫我们存钱或许是值得的。矛盾的是,有些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或许会为了存钱而借钱。我们在海得拉巴贫民窟遇到的一个女人告诉我们,她从斯潘达纳公司借了1万卢比(购买力平价621美元),然后立即将贷款存入一个储蓄账户。因此,她要向斯潘达纳公司支付24%的年利率,而从她的储蓄账户赚取约4%的利息。我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解释说,她的女儿已经16岁了,两年之后就会嫁人,而那1万卢比是女儿的嫁妆。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将支付斯潘达纳公司的钱直接存入她的储蓄账户,她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会有事情发生。
很明显,人们不应为了存钱而每天支付20%或更多的利息。设计一些具有小额信贷合同特色的金融产品,可以帮助很多人。一组研究人员与一家银行共同对菲律宾穷人进行研究,并开发出了这样一种产品:一种与每位客户储蓄目标绑定的新型账户。这一目标可以是一定数量的存款(客户要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会取款),也可以是一个取款日期(客户要承诺在这一日期之前不动用账户中的钱),由客户自由选择。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计划就会生效,银行就可以强制执行。这一账户的利率并不比普通账户高。在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中,每四人中约有一人同意开户。在开户者当中,2/3的人会选择取款日期目标,而余下的1/3则选择存款数量目标。一年之后,尽管每四人中只有一人开户,那些选择这一账户的人,其账户的余额比对照组(没有选择这一账户)平均多出81%。然而,实际效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小,因为尽管当时有不取款的承诺,但并没有推动客户存钱的动力,所以很多已开户的账户都处于休眠状态。
然而,大多数人宁愿不选择这样的账户。他们显然是在担心,自己或许无法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取款。迪帕和罗宾逊在肯尼亚便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很多人并未使用提供给他们的账户,有些人是因为取款手续费太高,不想将自己的钱锁死在账户中。这凸显了一个有意思的矛盾之处:有些方法可以解决自我控制的问题,但要利用这些方法,则常常需要一种原初的自我控制。在另一项关于波玛拉市场小贩的研究中,迪帕和罗宾逊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们注意到,很多小业主(或其家人)在生病时会丢掉生意,还要花钱买药。所以,他们想帮助人们专门存一笔钱,用于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或是购买预防性医疗产品(如消毒液或蚊帐)。他们联系了几家轮转基金的会员们,给了他们一个有锁的箱子,专门用来存入应急健康款。有些人(随机选择的)得到了打开箱子的钥匙,而另一些人则没有拿到钥匙:当人们因健康问题需要用钱时,这家非政府组织的职员会来为他们打开箱子。给人们一个保障健康的箱子有助于他们将更多的钱花在预防性医疗措施上,但给他们一个带锁的保障健康的箱子,结果恰恰相反,这有些出乎迪帕和罗宾逊的意料:他们根本就不会将钱存入箱子,因为他们担心在需要时会拿不到钱。
因此,意识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预见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遇挫折。
由于自我控制很难实现,自觉的决策者们会采取其他行动,减少自己将来受到诱惑的可能性。一个明确的策略就是,不存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就会把钱花掉:可能我们今天就经不住诱惑,这种关于诱惑的逻辑对于穷人或富人都一样,但后果对于穷人来说或许更为严重。
诱惑是生理需求(性、糖、脂肪类食品、烟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容易满足“受到诱惑的自己”。在决定是否存钱时,他们认为,任何为将来而存的钱都会用于实现长期目标。因此,如果糖和茶是一种诱惑物的原型,那么富人不太可能会有所困扰——他们并不是不会受到诱惑,而是无须担心多喝一杯茶就会花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这种效果会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加强,即穷人真正期望拥有的很多东西(如一台电冰箱或一辆自行车,或是自己的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都较为昂贵,而他们的手中只有一点点钱(穷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杯茶吧……”)。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对于穷人来说,自我控制更难实现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关于存多少钱的决定都很难做出,这些决定需要考虑到未来(对于很多穷人来说,想象未来可能是不愉快的),还要列出大量可能发生的事件,需要与配偶或孩子商量。我们越富有,这些决定就越容易做出。为了每周或每月都能存下钱,穷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然而,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因此,穷人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富人会根据其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这就会产生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值关系的S形曲线。穷人存的钱较少,因此他们的未来资源一般也较少。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他们就会存下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未来资源。最终,当人们足够富裕时,他们不再需要为实现将来的目标而存下那么多财富,这与中产阶层的情况不同(这或许是他们省下钱来买房的唯一方法)。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值之间的S形曲线。图8–1体现了泰国家庭1999年所拥有的资源与其5年后所拥有的资源的关系。这是一条平缓的S形曲线。今天较富有的人(拥有更多资源),明天一般会更富有,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这一关系曲线在资源处于很低水平时表现得很平坦,但在完全变平之前突然有所上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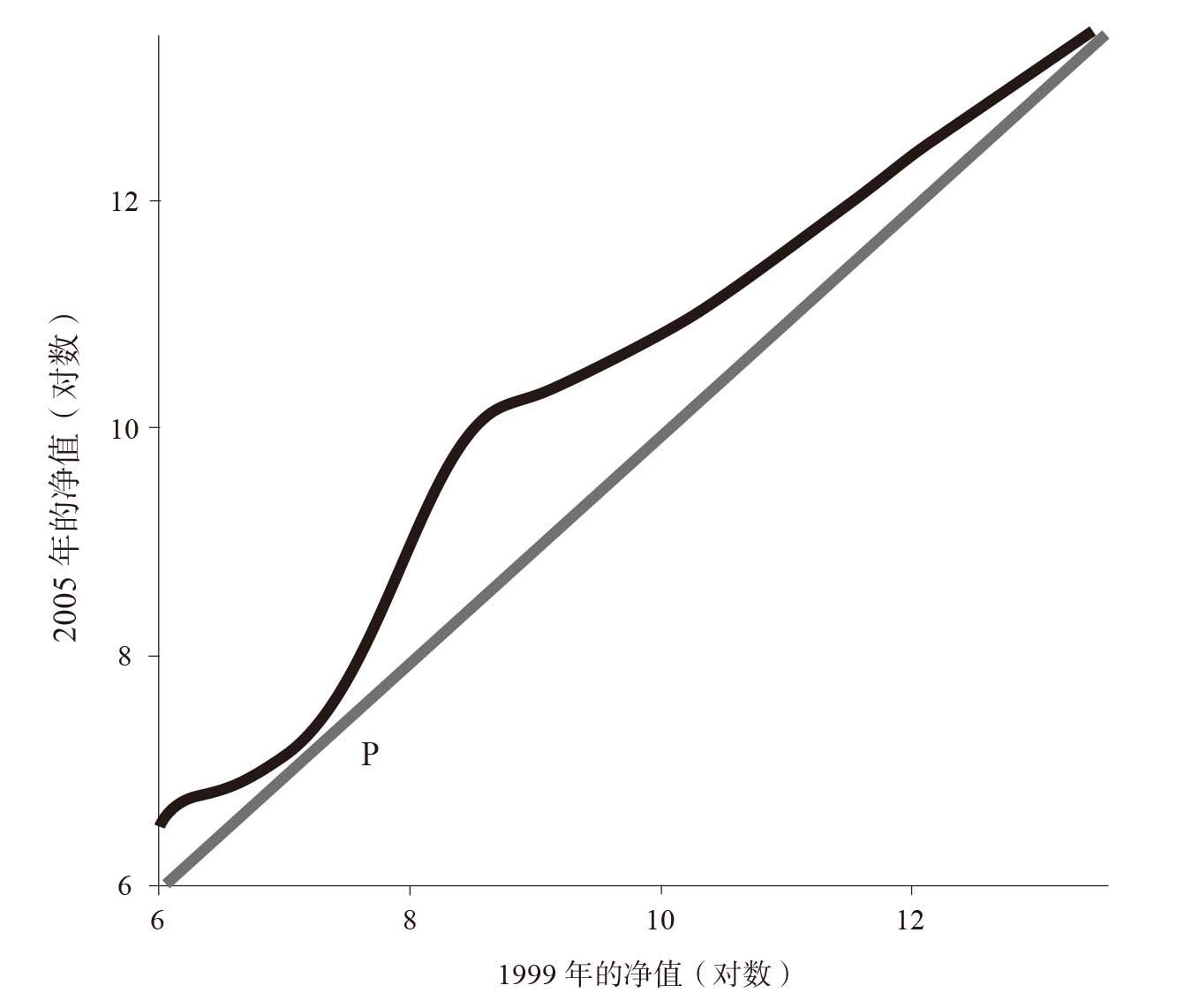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一S形曲线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那些从左边起步、财富曲线只到达45°角的人,他们的富裕程度不会超过这个点。他们的财富不会积累得更多——他们处于“贫穷陷阱”之中。然而,那些超过P点的右侧曲线正在存储更多的财富。穷人仍然处于贫穷状态,因为他们存的钱不够多。
存款行为关键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穷人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用作未来的投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一般会做出反映这一绝望心态的决定。这不仅可以解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还可以说明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水果小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迪安·卡尔兰完全还清了贷款。一段时期内,很多小贩都做到了没有负债;10周之后,菲律宾仍然有40%的小贩身无欠款。因此,这些水果小贩似乎有足够的耐心,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摆脱欠款。然而,几乎所有小贩最终还是会欠款,通常是由一场灾难(疾病、紧急需求)导致的,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并不能独立还清欠款。想要摆脱欠款与无法摆脱欠款之间的矛盾表明,自我控制很难发挥作用。
然而,乐观与希望却能够对此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你觉得自己一定能买下一直想买的那台电视机。在我们对斯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时,帕德马贾·蕾迪带我们到贡土尔市(该机构的创办地)贫民窟见她的客户——几个女人,她们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们听到她们在谈论,怎样通过削减茶叶、零食等花费改善她们的未来。
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都不同意借款购买消费品——有些机构甚至会努力确保其贷款用于购买一些赚钱的资产。然而,蕾迪认为,只要她的客户用这笔钱实现了任何长期目标,就足够了。在蕾迪看来,要想摆脱贫穷,首要的步骤就是对长期目标进行思考,并习惯为此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
在对斯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之前,我们问一些女性她们想在哪些方面省钱。其实,我们无须担心,蕾迪了解客户的所思所想。我们在第七章关于贷款的部分看到,获取小额信贷的最明显影响之一就是,减少在一些物品上的消费(茶叶、零食、烟酒等)。对于那些因该计划获取小额信贷的家庭,每个家庭每月在这些物品上的总消费减少了约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美元),或者相当于普通家庭消费的85%。就一份1万卢比的贷款(20%利率)来说,这方面消费的减少可以支付每月还款的10%左右。后来,我们在摩洛哥的农村地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客户削减了社会消费,并为自己存下了钱。
当然,就实现穷人的一些长期目标而言,小额信贷只是我们为他们想到的很多种方法之一。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或许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则是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讨论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或自然灾难的保险,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毁于一旦。或者为他们创建一种社会安全网络: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到一个特定范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支持,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没钱存活下去了。这些方法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鼓励人们存钱,减少人们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两方面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希望、保障及安慰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措施。我们都很容易过上一种安稳的生活,制定一些我们有信心实现的目标(一张新沙发、50英寸的平板电视、第二辆汽车等),寻求一些机构(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住房贷款等)的帮助。然后,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依据动力与规则行事。但实际上,人们总会担心,他们会宠坏那些懒惰的穷人。而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恰恰相反:当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很 多年前,在飞机上坐我们旁边的一位商人曾对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读完MBA回到印度,他的叔叔带他去体验一种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一个早晨,他和叔叔动身前往孟买股票交易所。然而,他们并没有进入交易所所在的那座现代化的大楼,他的叔叔让他观察坐在路边的4个女人,她们面向着交易所前方的那条路。这位商人和他的叔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观察着那4个女人。她们几乎什么也没做,但是当来往车辆不多时,她们偶尔起身从路上捡点儿什么,放入她们身边的塑料袋里,然后坐回原位。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叔叔问他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坦然承认自己一头雾水。于是,他的叔叔解释说,每天黎明之前,这几个女人都会去海边收集湿海沙,然后在交通繁忙之前将海沙平铺在路面上,当车子碾过路面的海沙时,车轮散发的热气会烘干海沙,而她们所要做的就是,偶尔起身捡起表层干燥的海沙。几天之后,她们就会积攒很多干燥的海沙,并将它们带回贫民窟,用由废旧报纸做的小口袋装好,拿到市场上去卖。当地妇女用干沙擦洗盘子。他的叔叔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所拥有的不多,那么就用你的聪明才智,做到从无到有。
贫民窟的女人为了谋生,会充分利用孟买的商业契机,这展现了穷人所具备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本书中,我们讲述了一些小企业主创新自强的故事。对于近期的小额信贷“社会交易”运动来说,这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因为,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穷人天生就具备企业家的潜质。因此,只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环境及在起步时的一点儿推力,我们就能够消除贫穷。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凯奇曾说过:“给贫穷社区一些机会,然后就放手。”
然而,或许还有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放手,穷人似乎并不会有所作为。自2007年起,我们一直与AL Amana(摩洛哥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共同评估小额信贷业务对农村社区的影响。这些社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正式的金融渠道。约两年之后,很明显,AL Amana并没有在农村实现预期的客户人数。尽管选择性有限,但对贷款感兴趣且具备条件的家庭仍然不到1/6。为了找到原因,我们同AL Amana的几位员工来到一个名为哈福莱特的村庄(那里没人贷过款),对那里的几个家庭进行了家访。我们见到了阿拉·本·希达,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希达还有4头牛、1头毛驴和8棵橄榄树。他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另一个儿子负责照看牲畜,而第三个儿子却整天无所事事。我们问希达,是否愿意贷款多买几头牛,让他的第三个儿子负责照看。他解释说,家里的地太少了——如果买更多的牛,可能就没有地方放牧了。在离开之前,我们问他是否需要贷款买点儿什么,他回答说:“什么都不用买,我们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把牛卖掉,还可以卖橄榄。这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几天之后,我们见到了AL Aman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福阿德,他是一个充满热情、极具才智的人,以前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曾因犯政治错误蹲过几年监狱,他一直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探讨了小额信贷的低需求问题,还特别提到了希达的故事——他确信自己不需要更多的钱。福阿德为希达设计了一个明确可行的计划。他可以贷款建一座牛棚,然后再买4头小牛,这样他就不用再到田里放牧了,可以在牛棚里喂养它们。8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将牛卖掉,并得到一笔丰厚的利润。福阿德认为,如果有人将这一切告诉希达,他一定会被说动,并会决定贷一笔款。
福阿德的热情与希达的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令我们颇为震惊。然而,希达并不甘于一直贫穷下去: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感到骄傲,这个儿子一直在接受护士培训,是军队里的一名护理人员。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有机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福阿德的想法是否正确,希达真的只需要得到一个商业指导计划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希达大半生都从事的养牛生意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世界著名的格莱珉银行,他常常将穷人称为“天生的企业家”。还有,已故的商业巨头普拉哈拉德也曾劝告商人们,应更加关注其所谓的“金字塔底”。这表明,在大企业和高等财政部门的参与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穷人有助于扶贫政策的实施。公共行动的传统策略已得到个体行动的补充,这些行动常常是由企业界的一些领导人做出的,主要是为了帮助穷人挖掘其企业家的潜力。
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有两个明确的原因甚至可以证明,穷人或许会发现更好的机会。第一,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更新颖。第二,目前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因此,他们称,创新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轻松摘到的果实,而且能够想象出穷人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
的确,每一家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很多成功客户的故事,其成功都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一次致富的非凡机会。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曾见过这样一些客户。在安得拉邦的贡土尔市,我们见到了一位斯潘达纳公司的客户,她通过收集垃圾并分类,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收垃圾的,处于印度经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用来自斯潘达纳公司的第一笔贷款,她还清了从一个放债人那里借的钱(利率很高)。她知道,从她那里买垃圾的公司会对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再卖给回收公司——例如废旧灯泡、塑料制品、肥料有机物都含有残留的铁和钨。于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她决定自己对垃圾进行分类。通过第二笔贷款及第一笔贷款赚的钱,她买了一辆手推车,这样她就可以收集更多的垃圾。由于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她让自己的丈夫也来帮忙。她的丈夫过去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在喝酒,现在则开始给她帮忙。这样一来,他们赚到了更多的钱。在获得第三笔贷款之后,他们开始从别人那里收购垃圾。当我们见到她时,她已掌控了一张很大的垃圾收集网络。她不再是一个收垃圾的,而是一位垃圾收集活动的组织者。而且,她的丈夫这时也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们看到他时,他正拍打着一块金属,表情严肃,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小额信贷机构会宣传他们最成功的借款人的故事,但这些企业家在没有接触小额信贷时就已经成功了。1982年,在中国浙江省的绍兴市,徐爱华是村里最优秀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与所有人一样,手里几乎没有现钱。然而,徐爱华非常聪明,村里决定送她去当地的一家时装设计学院学习一年(不过,当时每个人都穿着中山装)。村里认为,日后,她定能在乡镇企业中担任领导,这些企业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但是,当她接受完培训回到家时,当地的长者们犹豫了——毕竟她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因此,她无声无息地待在家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徐爱华不愿意闲着,她决定自己做点儿什么,但她的父母太穷了,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她借来一个扩音器,在村里走街串巷,说她可以教小女孩做衣服,只收取15元学费(购买力平价13美元)。她招收了100名学生,拿着收来的学费,她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还有当地国有工厂一些多余的布料,然后开始教学。在课程结束时,她留下了8名最优秀的学生,并开了一家服装店。女孩们每天早晨都背着自己的缝纫机(每个人都让自己的父母买了一台)来这里裁剪制衣。她们为当地工厂的工人制作工作服。一开始,她们都在徐爱华的家里工作,但随着生意的扩大,徐爱华培训并雇用了更多的人,她们就搬到了从村政府租来的一栋楼中。
到1991年,徐爱华积攒了大笔做生意赚来的钱,可以买60台自动缝纫机(价值54 000元,购买力平价27 600美元)。在8年里,她的固定资产总额增长了100多倍,每年增长80%。即使我们考虑到每年10%的通货膨胀率,(刨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每年超过70%的实际增长率也是令人震惊的。此时,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了。不久,出口合同接踵而至。现在,她的销售客户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贝纳通公司、杰西潘尼公司及其他一些大型零售机构。2008年,她首次向房地产领域投资2 000万元(购买力平价440万美元)。因为据她所说,她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大多数人则没有。
当然,徐爱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穷人创业精神的故事不在少数,穷人当中也不缺少企业家。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城市地区50%极度贫穷的人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即使在乡村极度贫穷的人当中,很多人也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从乌代布尔的7%到厄瓜多尔的50%),还有很多人经营着自己的农场。在这些国家中,贫穷程度较低的企业家人数是大致相同的。我们将这一情况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12%的在职人员称自己属于个体经营。就从事的职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人群相比,贫穷国家的大多数收入人群似乎更具企业家精神——穷人在这方面并不比别人差,这一看法激发了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创作了《亿万企业家》(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一书。
穷人企业主的人数令人印象深刻,一切似乎都对穷人成为企业家不利。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的保险、银行服务及其他廉价金融渠道。对于那些无法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借到足够钱的人,放债人是自由贷款的主要渠道,他们每月需要支付的利率为4%或更高。因此,穷人很难为经营一种合适的生意而做出必要的投资,他们更容易受到来自这种生意的附加风险的影响。然而,他们仍像富人那样努力挤进商界,这一事实常被认为是其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然而,即使在支付高昂的利率之后,穷人仍能够还清贷款(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几乎不会违约)。这一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每一卢比的投入一定能获取更高的回报。否则,他们就不会借钱了。这表明,他们所投资的领域具有高回报率。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年能够还款50%,而即使你投资道琼斯也不一定能收回这么多钱,何况在当今这一时期,人们投资的长期平均收益每年也只有9%。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借钱。或许,只有少数收益较高的企业家会这么做,而其他所有人的收益都很低。然而,在斯里兰卡开展的一个计划却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很多小企业主——零售店、修理店、蕾丝制作者等——受邀参加一次抽奖,中奖者可以得到一笔价值1万或2万卢比(购买力平价250美元或500美元)的商业赠款。
这笔赠款用全球标准来衡量并不算多,但对这些企业来说也不算少;对于很多人来说,250美元是他们起家的全部资金。中奖者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笔钱。对于普通生意者来说,250美元的第一笔回报是每年60%以上。随后,墨西哥也在小企业当中开展了这一活动,其回报率更高,每月达到10%~15%。
孟加拉国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计划,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果表明,只要得到恰当的帮助,即使最穷的人也能成功经营一些小生意,并通过这些小生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这一计划中,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挑选了一些最穷的人,这些人大多依靠施舍生活。小额贷款机构一般不会贷款给这样的客户,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经营某种生意,也没有能力定期偿还贷款。为了帮助这些人起步,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给他们一种资产(一对奶牛、几只山羊、一台缝纫机等),还有几个月的小额经济补助(用作运营资金,确保他们不会将资产卖掉),还为他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定期开会、开办扫盲班或鼓励他们每周存一点儿钱。该计划的影响因素目前正以随机对照实验的形式在6个国家展开,在该计划启动之前,我们对一些为此而挑选出来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听说了很多有关危机与绝望的故事:丈夫是一个醉汉,常常打他的妻子;有人年纪轻轻就在事故中丧生,留下一家人无人照看;一个寡妇被她的孩子遗弃等。但两年之后,差别显而易见:与其他未参与该计划的极度贫穷家庭相比,参与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牲畜及其他资产。他们每月的总支出上涨了10%,食品支出是增长最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不再抱怨吃不饱饭。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的人生观似乎也有所改变,在描述自己的健康、幸福及经济状态时更积极。他们可以存下更多的钱,对于资产管理也信心满满。
当然,两年之后,他们的消费水平只上涨了10%,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很穷。但最初的馈赠及支持似乎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能够得到机会,即使遭受过重创的人,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极度贫穷。
看到这么多人在面临困境时都成了企业家,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尤努斯和福阿德投资于穷人的热情。然而,这一现状下仍然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很多穷人都在经营着生意,但他们经营的都是一些小生意;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生意赚不了多少钱。
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穷人经营的大部分生意几乎都不雇用员工,平均员工人数从摩洛哥农村的0人到墨西哥农村的0.57人。这些小生意的资产一般也非常有限。在海得拉巴市,只有20%的生意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或交通工具,最常见的资产就是桌子、尺子和推车。
显然,如果这些人的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贫穷了。问题在于,尽管社会中不乏垃圾收集者以及徐爱华之类的例子,但穷人经营的大多数生意都难以发展到这种程度(有自己的员工及资产)。例如,在墨西哥,2002年时,每天生活费低于99美分的人15%有自己的生意,而三年之后,当这些家庭再次接受家访时,只有41%的生意仍在运营之中。在两个阶段接受调查的穷人企业当中,1/5的企业在2002年时没有雇用员工,到2005年时雇用了一位员工。然而,在2002年时雇用了一位员工的一些企业,到2005年时却没有员工了。同样,在印度尼西亚,只有2/3的穷人企业能够存活5年。而且,在这些存活下来的企业当中,雇用一位员工以上的企业在5年间并未增加。
穷人企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般很难挣到很多钱。我们对海得拉巴市小生意的赢利及销售情况进行了估算:平均销售额为每月11 757卢比(购买力平价730美元),平均每月赢利(刨除租金)为1 859卢比(购买力平价115美元)。在我们关于海得拉巴市的调查数据中,15%的生意在过去一个月里都在赔钱。我们还对家庭成员付出的时间进行了评估,他们的报酬率低得只有每小时8卢比(即使他们一天干8小时,也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平均收入甚至有些入不敷出。在泰国,这种规模的企业在扣除经营成本、不计算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其平均年收益为5 000泰铢(购买力平价305美元)。7%的家族企业在过去一年里赔了钱,而这还没有刨除家庭劳动力的价值。
穷人经营的生意只能产生较低的利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小额信贷似乎很难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果穷人经营的生意都不赚钱,那么给他们提供一笔做生意的贷款根本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不过,我们不是刚刚才说过,投资于这些小生意的收益很高吗?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关于“收益”一词的两种用法。经济学家将收益分为以一美元计算的边际收益和一种生意的总体收益。以一美元计算的边际收益可以回答的是:“如果你多投资一美元或少投资一美元,那么你的总收入除去所有运营成本(不包括利息)后是怎样的?”边际收益将决定你是否应减少投资(或增加投资):如果少投资一美元可以使你少借一美元,你就可以少还4%的本金及利息,那么在边际收益少于4%的情况下,你就会愿意进行投资。因此,如果人们每月借款的利率为4%,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边际收益至少为4%。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穷人所经营的生意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
另外,一种生意的总体收益是指除去所有运营花费(材料成本、付给员工的工资等)之后的总收入。通过考察总体收益,你可以决定是否应涉足这种生意。如果这一收益不足以抵消你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及成本,而且你认为情况不会很快得到改善,那么你就应停工。
然而,一个矛盾之处就是,在边际收益很高的情况下,总体收益可能会很低。在图9–1中,曲线OP代表公司投资总量(以横轴OI衡量)与总体收益(以纵轴OR衡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生产技术”(production technology)。相对于K的投入资金,曲线的最高点就代表总体收益。加入边际收益会使曲线高度产生变化,即从K变为K+1。由此我们得知,当公司的投资增加时,总体收益也会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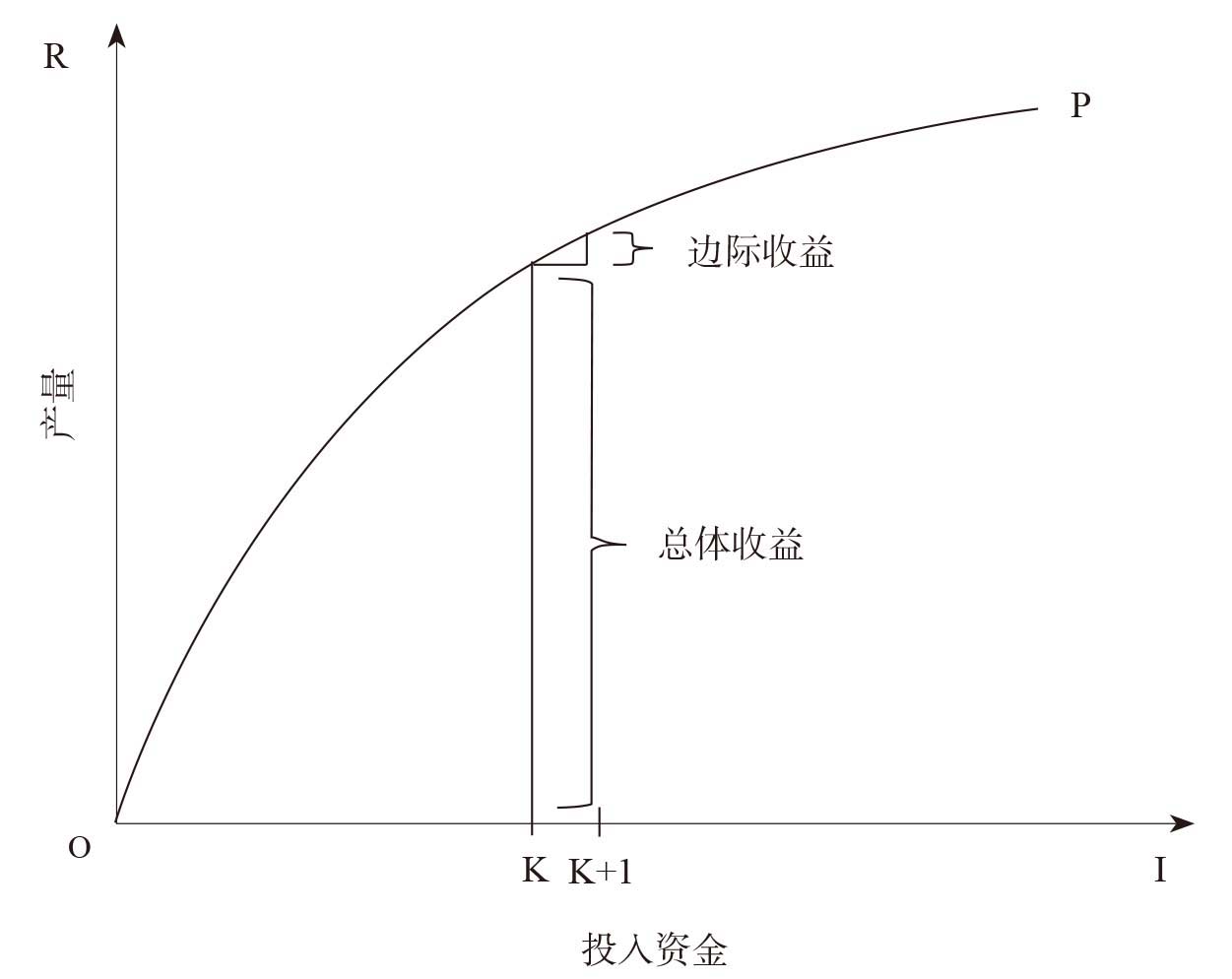
图9–1的曲线很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曲线L:收益起初很高,然后逐渐降低。当投资小时(最靠近O),OP线最陡,然后逐渐变平(慢慢靠近P)——这就意味着,当最初的投资较小时,增加投资就会最大化地增加收益,而这种增长最终会逐渐消失。换句话说,当投资较少时,边际收益就会很高。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假设某人刚刚在家里开了一家店。她花了点儿钱做了一些货架和一个柜台,之后手里就没钱进货了。所以,她这笔生意的总体收入为零,并不足以抵消做货架的花费。然后,她的妈妈借给她1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美元),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些饼干,放到货架上卖。邻区的孩子们看到这种饼干,正是他们喜欢吃的那种,于是跑来买走所有的饼干。她赚了15万印度尼西亚盾。就她妈妈提供的贷款来说,每一印度尼西亚盾的边际收益为1.5印度尼西亚盾或50%净收益,这种状况如果能持续一周也不错。然而,总体收益只有5万印度尼西亚盾——这并不足以抵消她所付出的时间,还有做货架和柜台的成本。
接下来,这位店主又贷款300万印度尼西亚盾,买来足够的饼干和糖果,摆满了整个货架。于是,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都来光顾,她一下子卖掉了很多货物。但是,在一些新顾客到来时,有些饼干已经开始变质了,卖不掉了。不过,她在一周之内赚了360万印度尼西亚盾,此时的边际收益低于50%——她的投资增长了30倍,但她的总收入只相当于以前的12倍。不过,此时她的总体收益达到了6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07美元),足以将这一生意维持下去。
对于很多穷人来说,这就是现实。那些空空的货架并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北部古尔伯加镇郊区(距海得拉巴市车程约5小时)看到,一家商店的存货就是很多摆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的空塑料罐子。不一会儿,我们就列出了它的全部存货清单。
印度卡纳塔克邦农村一家普通商店的存货清单
1罐美味小吃
3罐软糖
1罐加1小袋包装硬糖
2罐鹰嘴豆
1罐速溶咖啡
1袋面包(5片)
1袋扁豆小吃
1袋薄脆饼干(20块)
2袋饼干
36根卫生香
20块力士香皂
180份潘帕拉(槟榔和嚼烟的混合物)
20袋茶
40袋好地粉(姜黄粉)
5小瓶爽身粉
3包香烟
55小袋比迪斯(细细的香烟)
35大袋比迪斯
3袋洗衣粉(每袋500克)
15小包饼干(曲奇)
6袋独立包装的洗发剂
我们对这家商店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拜访,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两位顾客。一位只买了一根香烟,另一位则买了几根卫生香。显然,如果这家商店稍稍扩大经营规模,它就极有可能产生很高的边际收益;如果它能够进一些同村其他商店没有的货物,那么它的边际收益就会更高,但总体收益却很低:在销售量偏低的情况下,整天经营着商店并不值得。
在发展中国家,每个村庄都会有几家这样的商店,而在大城市,这种商店则有成千上万家。很多商店都在销售着相同的货品,与卖水果、椰子及零食的小摊毫无二致。每天早晨9点,走在印度贡土尔市最大贫民窟的大街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女人在卖一种叫作“dosas”的薄饼。这种饼是用米和扁豆做成的,堪称印度南部的“牛角面包”。她们在薄饼上涂上辣酱,用一张报纸或香蕉叶裹起来,每张薄饼售价1卢比(购买力平价约5美分)。我们计算了一下,每6户人家,就会有一户卖薄饼的。结果,这些女人一直在等着有人来买薄饼。很明显,如果她们能够几个人合卖,她们会赚到更多的钱。
这就是穷人和他们所做生意的矛盾之处:他们精力充沛,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努力地做着白手起家的生意。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很小的生意上,而且他们同周围很多其他人都在做着相同的生意。结果,他们失去了过上一种富裕生活的机会。孟买那些富有创意的拾沙女们,发现了利用现成资源赚钱的机会:一些自由的时间和海滩上的沙子。但商业精英没有指出的是,尽管她们有这样的聪明才智,但这种生意几乎赚不了几个钱。
这类生意虽然规模较小,边际收益很高,但其总体收益常常很低。然而,这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只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边际收益就会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总体收益很容易,那么,为什么这些小生意发展得都很缓慢呢?
一部分答案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生意都借不到多少钱,而且借钱的代价非常高昂。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首先,我们看到,尽管有上百万的小额信贷借款人,但很多有机会贷款的人都选择不去贷款。本·塞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饲养奶牛,本来可以通过小额信贷来扩大经营,但他决定不这样做。即使在海得拉巴市,具有借款资格的家庭与当地几家颇具竞争力的小额信贷机构的签约率仅为27%,而且只有21%的家庭曾办理过小额信贷业务。
即使那些每天生活水平约2美元的人也可以存钱,古尔伯加的那家商店便是如此。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海得拉巴市附近,对于处在这一消费水平的人来说,他们每月花在医疗上的钱约占总支出的10%;而对于那些每天生活水平低于99美分的人来说,这一比例约为6.3%。如果这位店主将那余下的3.7%用来扩充存货,而不是用作医疗费用,那么一年之内他就能使店中的存货量翻一番。或者,这家商店还可以削减烟酒的进货量,这样他们就能每天节省约3%的人均开支,在15个月之内将存货量翻一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斯里兰卡的实验明确地描述了这一事实,即资金匮乏并不是扩大生意的唯一障碍。那些用250美元赚了很多钱的企业家,他们的边际收益比美国最成功的公司都要多。然而,关键在于,按绝对价值计算,与拿到250美元的企业家相比,拿到500美元的企业家们所赚的钱不会增长得更多。部分原因是,拿到500美元的企业家不会将钱全部投到生意中,他们只会投入一半,余下的钱他们会用来为自己家里买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店主对这么高的边际收益有更好的用途吗?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斯里兰卡的小企业主们确实投入了第一笔资金,如果他们选择不再投入第二笔资金,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意没有能力赚回这笔资金了:投入全部资金会将一家普通企业的股本增加两倍,这时,企业还需要再雇用一位员工,或者找到更多的存货空间,来维持自己的经营,而这样就会花掉更多的钱。
因此,穷人所做的生意之所以会发展缓慢,部分原因仍然在于他们所做生意的性质。图9–1中的倒L形曲线表明,即使边际收益很高时,总体收益也可能会很低。图9–2显示了图9–1曲线的两种形式:第一,OP线一开始很陡,但很快就平缓下来;OZ线一开始上升得不快,但一直延伸到很长。
在现实世界中,穷人所做生意的利润就像曲线OP一样,一家小公司很容易发展起来,但其发展潜力很快就会耗尽。这与小店主的例子很相似:一旦你把家里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开商店,并且一天在那里工作几个小时,如果你有足够的货物填满整个货架,那么相对于无货可卖的情况,你的利润就会更高。不过,一旦你的货架已被填满,进一步扩大经营或许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边际收益,用来支付高昂的贷款利率。因此,所有的生意规模都很小。另一方面,如果情况像OZ线一样发展,那么扩大经营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整个世界更像OP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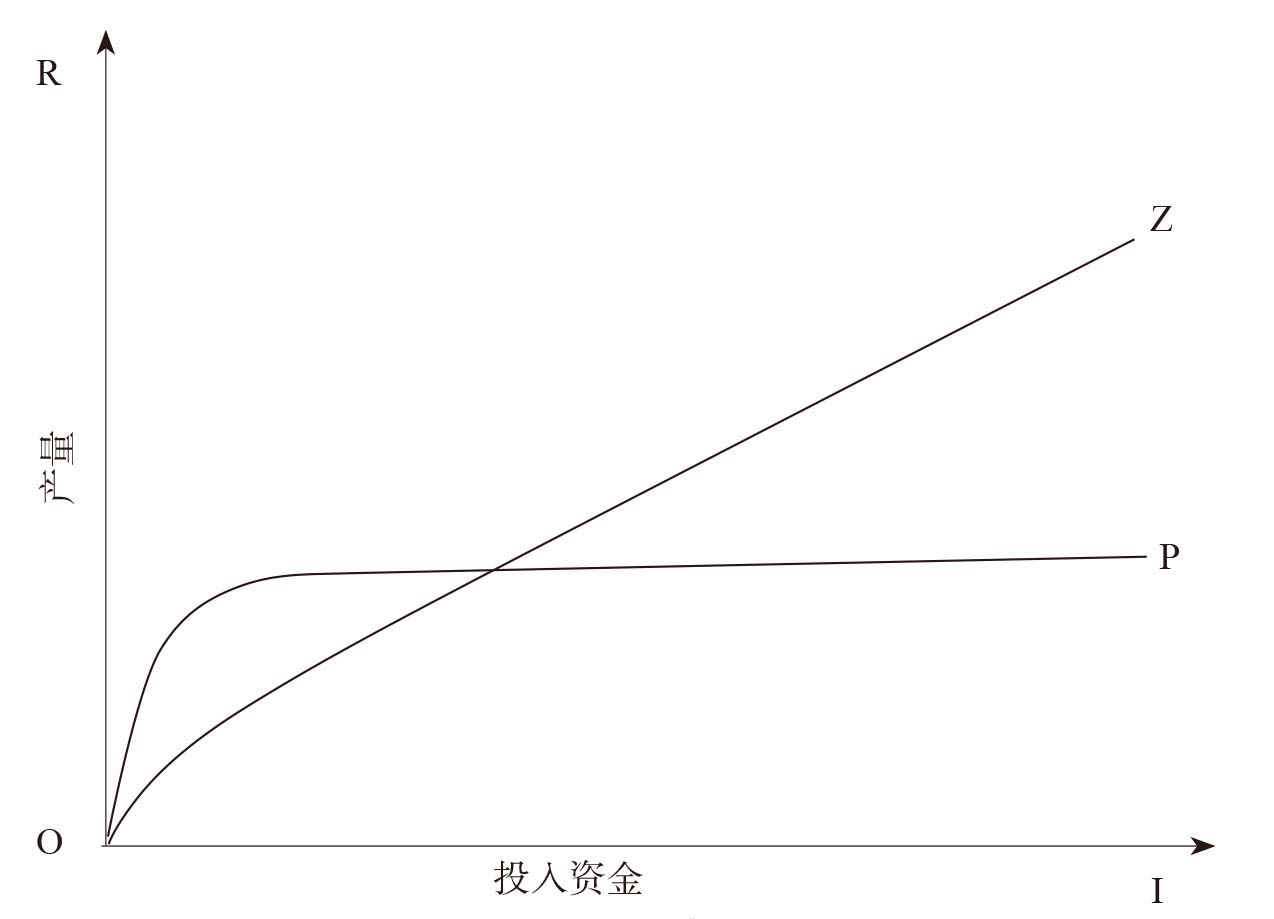
当然,我们知道,情况不会总像OP线那样,否则也就不会有大公司了。或许,店主、裁缝和小贩的生意就像OP线,但某些其他类型的生意也会用到更多的生产资本。如果一个人能够买到合适的设备,那么他就能经营一家大型零售连锁店或纺织工厂。不过,这样做需要具备某种特殊技能或一大笔前期投资。你可以在一间车库里成立微软公司,然后不断扩大经营规模,但要想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站在某种新产品的前沿地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另外一种选择是,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使你的公司能够大规模运营起来。徐爱华——那位以一台缝纫机白手起家的中国女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服装王国。当她得到了第一笔出口订单时,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点,那么她很快就会被当地市场吞没。为了完成出口订单,她需要建立一家现代化的工厂,具备一些自动化的缝纫机。这样一来,她需要投入的资金比公司初期的资本大概多了100倍。
图9–3代表了这两种生产技术的观点。左边是OP线,右边是一种新的生产技术OR,这条线一开始没有产生利润,但在小额投资之后,则产生了较高的利润。注意,为了画出一条连接线,我们用粗体显示了OP和OR的部分线段。OR线代表投入特定资金的实际利润。如果你只想投资一点点,那么你应该投资OP,不应投资OR,因为OR在刚开始时不会产生利润。如果你的投资较多,那么OP就不是一笔好交易,在一段时期内,其边际收益都会很低。然而,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钱,你就应转向OR。这就是徐爱华的经历:她一开始走的是OP路线,那时她只有一台二手缝纫机,后来她转向了OR线,随之而来的是自动缝纫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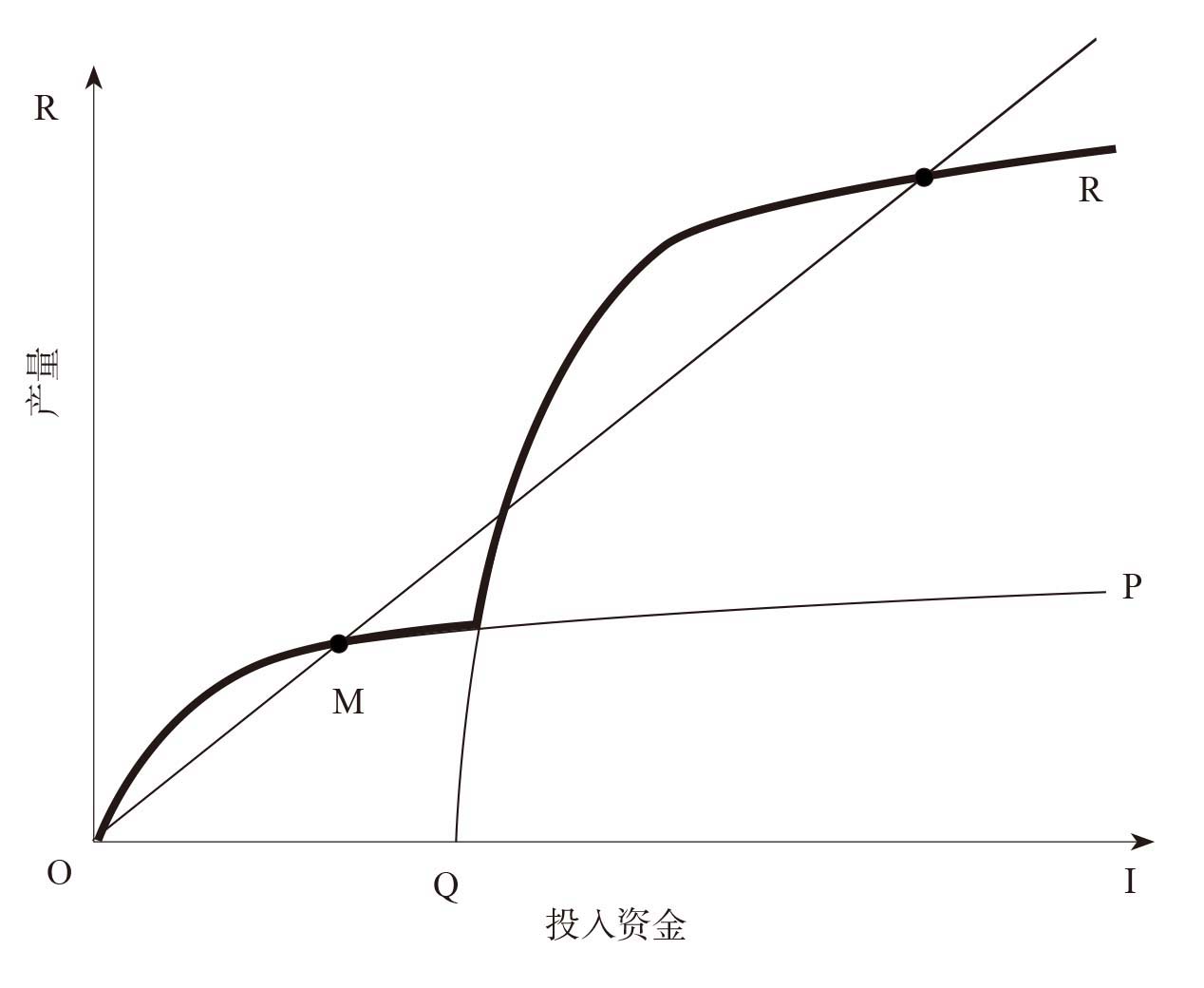
OR线很像S形曲线,不是吗?中间有一个驼峰,这是商家为了赚钱要到达的点。OR线再现了常见的S形曲线矛盾:投资一点儿就赚一点儿钱,这样一直都不会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或者越过驼峰,多赚一些钱,然后加大投资,从而赚得更多。关键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会选择越过驼峰。尽管他们可以获取小额信贷,但这些小企业主们却得不到足够的贷款。此外,到达这一点或许还需要一些管理或其他方面的技能,而这是小企业主们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们的生意一直都处于小规模状态。面临边际收益的前期增长,同一个小企业主往往会选择同时经营3种不同的生意,而非努力扩大其中任何一种生意的规模。例如,他会在早上卖多萨饼,白天卖萨里斯饼,晚上穿珠子制作项链。
但是,徐爱华是怎么做到的呢?她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连续8年每年扩增70%的设备。因此,在去除发给工人的工资之后,她的利润至少是设备价值的70%,所以她的总体收益肯定很高。我们认为,这不仅表明徐爱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还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很大的状况,因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时。
穷人无法扩大经营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太难做到了:他们借不到足够的钱跨越驼峰,存款额达到那个数目会花费过长的时间,除非他们的生意能够产生很高的总体收益。例如,你用100美元开了一家公司,然后像徐爱华一样,你需要投入100倍的资金(1万美元)用来购买新机器。如果你每投入1美元赚到了25%的赢利,而你将这部分赢利再次投入。一年之后,你就需要投入125美元;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增至156美元;三年之后,你需要投入195美元。那么,你需要22年的时间跨越驼峰、买到机器。如果你要将一部分钱用于过日子,只存下了一半的赢利,那么你就需要将近40年才能实现目标。而且,这还不包括做生意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
此外,一旦小企业主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S形曲线的底部,而且永远也赚不到那么多钱,那么他们更很难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意。假如一位企业家处于图9–3中的M点以下,那么他可以通过攒钱提高进货量,从而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超越M点。这值得吗?即使他有了想要的一切,他的生活可能也不会发生积极的改变。因为他的生意注定是这种小规模,不会赚到太多的钱。因此,他可能会将自己的注意力及资源用来做其他事情。
同样,相对于中产阶级来说,穷人的存款或许会更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存款不够实现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消费目标,他们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意投入那么多(不仅是钱,还包括情感投资和智力投资),何况这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本·塞丹、摩洛哥农民和福阿德之间在观点上的差距。福阿德或许是正确的,本·塞丹没想到可以在谷仓中养牛。或者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但可能一想到仅仅为了4头奶牛,就要贷款,还要建造一个新的牛棚,而最终还是要将牛卖掉,就会觉得这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了——毕竟,他们一家人还是那么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正确的:福阿德的生意模式仍然可行,而本·塞丹不值得那样去做。
大多数小企业主们并不会全力以赴地赚取每一分钱,这也能够说明,一些企业的培训计划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不过,现在很多小额信贷机构都建议客户去参加这类培训。在每周会议上,客户们都会学到怎样更好地记账、怎样管理存货清单、怎样了解利率等。这样的计划在秘鲁和印度的研究中有所评估。两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企业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他们的利润、销售额或资产却并未发生变化。这些培训计划的动力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这类生意特别不好经营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不热衷于这类生意,那么这种培训毫无帮助也就在人们意料之中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尝试了另一种培训计划,作为常规培训模式的辅助,这一种简化的课程建议企业家们关注简单的“手指规则”(如将生意花费与家庭花费进行区分,支付给某人固定工资)。这些培训的效果也并不明显,但为企业家们提供一些简单的小窍门,的确有助于利润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愿意采用这些经验原则,而且他们其实是简化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向生活索要更多的智力资源。
这样看来,我们不免要对“普通的小业主都是天生的企业家”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所理解的企业家是,他的生意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他有能力承担风险,并在工作中很努力,即使在逆境中也会全力以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人中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意注定不会发展起来,也不会赚到很多钱。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穷人还要自己做生意呢?我们从帕克·阿万和他的妻子那里找到了答案。这是来自印尼万隆贫民窟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用父母家里的一间屋子开了一家小店。帕克·阿万是临时建筑工人,但他常常找不到活儿干。当我们2008年夏天见到这对夫妇时,帕克·阿万已经失业两个月了。由于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人需要额外的收入,他的妻子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她想找一份工厂的工作,但她资质不够,工厂需要年轻、未婚或是有经验的工人。而阿万的妻子没有这样的工作经验,因为她念完高中后就开始学习当秘书,但最后没能通过秘书考试(这是找工作时所必需的),所以她最终放弃了这个职业。做点小生意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点小零食,然后拿到市里去卖,但她想找一份可以在家里做的工作,这样就可以照顾孩子了。因此,阿万从一家合作社得到一笔贷款,夫妻二人开了一家小店,不过在他们附近50码内还有两家商店。
阿万和妻子并不喜欢做生意。他们本来可以从合作社得到第二笔贷款,然后扩大他们的小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不幸的是,第4家商店出现在了他们的邻区,由于这家店商品齐全,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威胁。我们见到他们时,他们正想再贷一笔款购置更多的货物。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就是,长大后得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立业冲动被更多地展现了出来,穷人的事业似乎就是想办法买到一份工作。很多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下去,是因为家里有人时间较为充裕,这通常是女人,她常常要一边照看生意,一边做家务。我们尚不清楚,当做生意的机会出现时,她是否总能有自己的选择。因此,很多业主(尤其是女业主)并不喜欢做生意,而且害怕扩大经营。或许这可以解释,当斯里兰卡的女业主拿到250美元用于投资生意的钱时,很多人选择用这笔钱做些别的事情。这与我们之前遇到的男业主不同,他们会将钱用于投资并获取高回报。或许,穷人所做的很多生意并不是他们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是某些失败的经济模式的演绎。他们周旋于这些经济模式之间,努力地付出着。
在对全球穷人展开的调查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你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是什么?”结果令人震惊。无论我们在哪儿提出这个问题,穷人最常见的梦想就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政府职员。例如,在乌代布尔的贫穷家庭当中,34%的父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政府教师,41%成为非政府教师,18%成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职员。对于女孩来说,31%的父母希望女儿成为一位教师,31%希望她找到一份政府工作,19%希望她成为一名护士。穷人并不期望孩子成为企业家。
对于政府工作的特别强调表明穷人对于稳定的一种向往,因为这类工作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一般都非常稳定。而且,实际上,工作稳定似乎是中产阶层与穷人之间的一个界限。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中产阶层更可能会有一份按周或按月支付工资的工作,这是区分临时工与固定工的一种原始方法。例如,在巴基斯坦的城市地区,每天生活费不高于99美分的雇员按周或按月领工资的占74%,而每天收入为6~10美元按周或按月领工资的占90%。在农村地区,44%的穷人有固定工资,而64%的中产阶级有固定工资。
是否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在乌代布尔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低于2美元。但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村庄,那里的生活显然相对富裕:屋顶是铁的,院子里有两辆摩托车,还有整洁大方、穿着校服的孩子。原来,村子附近开了一家锌工厂,村子里的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该厂工作。在其中一个家庭里,身为一家之主(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父亲在工厂的厨房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了工厂的车间。他的儿子是村里第一批读完高中的8个孩子之一。这个孩子毕业后到这家锌工厂上班,而且有望在父亲退休前当上领导。他的两个儿子都读完了高中,两个女儿也在出嫁前读完了高中。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锌工厂建在这一地区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开启了一个人力资本投入的良性循环,引领他们在就业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
安德鲁·福斯特和马克·罗森茨维格的一项研究表明,工厂就业对于印度农村工资增长的促进并不仅限于此。在20世纪60年代至1999年期间,印度的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而村庄附近的工厂就业率也得到了提升,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投资政策的倾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9年期间,印度农村工厂就业率增长了10倍。1999年,在福斯特和罗森茨维格所研究的村庄中,约有一半村庄附近都有一家工厂,而且这些村庄中10%的男性劳动力都就职于工厂。这类工厂一般位于村庄中,起步工资较低,而这类工厂就业率的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甚至超过了由著名的绿色革命引发的农业生产力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此外,工业发展给穷人带来的收入也不够合理,因为即使对于那些低技能的人来说,更高报酬的工作他们也能胜任。
这种工作将为得到该工作的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与穷人相比,中产阶层在医疗与教育上的支出更多。当然,从原则上讲,有耐心、勤奋的人可能更愿意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投资,让他们有能力找到好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这并非答案的全部,而且这种消费模式与另一个事实有关,即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会通过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一项针对墨西哥儿童(他们的母亲都在出口工厂工作)身高的研究表明,一份好工作具有无穷的力量。出口工厂常常以剥削人、工资低而著称。然而,对于很多连中学都没上完的女性来说,在这里工作比在零售业、食品业及交通业工作更好,因为与出口工厂相比,那样的工作工资不会更高,但工作时间却更长。耶鲁大学的戴维·阿特金对两组母亲的孩子在身高上进行了比较,第一组母亲所在的城镇开了一家出口工厂,而另一组母亲所在的城镇则没有这种工厂(在该母亲16岁时)。结果显示,第一组母亲的孩子比第二组母亲的孩子要高得多。这一对比非常明显,同时也解释了贫穷的墨西哥孩子与正常成长的美国孩子在身高上存在差距的原因。
此外,阿特金指出,出口工厂的工作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不足以解释身高上的差异。或许,由于人们知道自己每个月都会得到一份收入(不仅仅是工资本身),因此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控制感,正是这种控制感使这些女人注重建立自己与孩子们的事业。或许,这一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区分穷人与中产阶层的重要依据。阿特金研究的主题“为将来而努力”巧妙地总结了这一观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详细举出了几个事例,说明风险对于家庭行为的影响: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贫穷家庭也会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降低风险。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或许是更深层次的结果:对于人们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时可能需要具备一种稳定感。至于那些看不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人,他们可能总是不愿继续努力,其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很多家长认为(或是误以为),教育所带来的好处呈S形曲线。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不能持续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教育投资对于他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怀疑自己将来承担孩子学费的能力——比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意可能会亏损——那么他们就可能认为,这种投资根本不值得一试。
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做更多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因此,如果家里的某位成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学校会更愿意接收他们的孩子;医院会为其提供更昂贵的治疗,因为医院方面认为,他们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投资自己的生意,谋求可能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做的事情。这种观点常常会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好工作可能是代价很高的工作,也就是较为少见的工作。不过,如果好工作意味着,孩子们生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可以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那么或许值得减少这类工作的数量。
由于大多数好工作都在城市里,所以搬家就成为改变家庭生活水平的首要步骤。2009年夏,我们在印度海得拉巴市的贫民窟结识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告诉我们,她从没上过学,16岁就生下了女儿。女儿上过学,但读完三年级就辍学了,不久便嫁人了。但她的第二个儿子正在读MCA(Master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我们从没听说过MCA,于是问她那是什么(我们以为那是某种专业学位)。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她的儿子出来为我们解释,那是计算机应用学硕士。在这以前,他已经获得了计算机学士学位。他的哥哥也已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私营企业办公室的工作。而最小的孩子正在读中学,也准备着报考大学。如果能得到一份穆斯林优惠贷款,家里人都希望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
那么,从女儿辍学到第一个儿子高中毕业,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这个家庭改变了其对于孩子的期望?父亲已经从军队退役,但通过军队的关系,他在海得拉巴市找到了一份国有公司的保安工作。由于他有了工作,不需要频繁迁移,于是一家人(除了他已经出嫁的女儿)都搬到了城里。海得拉巴市有很多不贵而优质的穆斯林学校,这是因为在1948年之前,当地还属于半独立的穆斯林王国。儿子们都去上学了,因此他们都发展得很好。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采取这一策略呢?毕竟,大多数城市的学校都比较好,即使是那些不具备海得拉巴市独特历史的城市。而且,穷人(尤其是贫穷的年轻男人)总会搬到城里找工作。例如,在我们采访的乌代布尔农村家庭当中,6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过去一年到城里工作过,但他们很少有人会迁居很长时间——平均只有一个月,只有10%的人的迁居时间在三个月以上。即使在国内,永久迁居也较为少见。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极度贫穷家庭中有一名成员需要为工作而迁居的比例为:巴基斯坦6%,科特迪瓦6%,尼加拉瓜6%,秘鲁将近10%。临时性迁居的影响之一就是,对雇主来说,没有必要将这些工人转为固定工,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特殊培训;他们一生都在打零工。因此,他们的家人不会搬到城里住,也不能上城里更好的学校,更无法得到一份固定工作所带来的心灵的宁静。
我们问一位来自奥里萨邦的流动建筑工人(他当时正在回家路上),为什么不在城里停留更长时间。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家搬到城里,那里的住房条件太差了。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离家太久。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城市很少会为穷人制订住房规划。结果,穷人不得不挤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常常是在湿地或垃圾堆里。相比之下,即使是最贫穷的人所住的村庄,都是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房屋宽敞、孩子们有嬉戏之地的。那里的生活可能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对于那些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那也是他们的朋友所居住的地方。此外,对于一位单身男性来说,如果他要在一个城市住上几周或数月,那么他并不需要去寻找真正的住所。他可以睡在大桥或某处的天篷下面,或是住在自己熟悉的商店或建筑工地。他可以把租金省下来,多回家几次。然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过这种生活。
这样做同样存在风险:假如你想花钱将一家人都搬到城市里去,那么你就只有丢掉工作了。的确,如果你还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及足够的积蓄,你又怎么搬得起这个家呢?而且,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当然,城市里面的医疗条件更好,但谁会陪你去医院?在你急需用钱的时候,谁来借钱给你呢?只要你的家还在村子里,那么即使你在城市里生病住院,你仍然可以借助你在村子里的关系。如果你拔掉了自己在村子里的根,搬到了城市里,结果会怎样呢?
因此,你更容易搬到有熟人的城市。当你们初次到达那里时,他们可以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住所;如果家人突然生病,他们也会来帮忙,还会帮你找一份工作——给你一份介绍信或是他们自己雇用你。例如,凯文·孟希发现,墨西哥村民会移居到别的村民定居的城市,即使最开始的那轮移居完全出于巧合。如果你在某一城市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或是其他稳定收入的渠道,那么搬过去显然更加轻松。来自海得拉巴市的穆斯林家庭二者兼具——一份军队养老金和一份工作。在南非,如果年迈的父母得到一笔养老金,他们的孩子就会永久地离开家里,搬到城市。养老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他们以此支付自己迁居付出的代价。
那么,怎样获取更多的好工作?显然,如果你能轻易搬到城里,那么,找到好工作也不成问题。可见,城市土地使用及低收入住房政策显然很重要。此外,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包括公共补助及市场保险)通过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可使移居变得更简单。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搬到城里住,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不仅大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好工作,较小的村镇也要提供就业机会。要实现这一点,城市与村镇的工业基础设施都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善。管理环境对于创造工作机会来说也很重要:劳动法对于安全保障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劳动法过于严格,导致没人敢雇用员工,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鉴于生产技术的S形曲线性质,信贷或许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要创立更多的公司,从而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这需要更多的资金,但这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普通业主所负担不起的。第七章关于信贷的部分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怎样让金融部门贷款给这类人群。
或许可以利用政府资源,如通过向中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从而创立足够多的大公司。中国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国有企业(或至少是部分国有资产,如设备、土地及大楼)被员工承包、管理,这也是朝鲜工业政策较为明确的一部分。这可以启动一种良性循环:较高的稳定工资为工人提供了经济资源、心理空间及必要的乐观心态,他们既可以用其为孩子投资,又可以用其储存更多的资金。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使人们更容易获取贷款,加上自己的存款和才华,他们最终才能雇用员工,创立自己的大企业。
因此,真的有10亿穷人企业家吗,就像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或是有公益头脑的商业巨头所确信的那样?或者,这只是因我们对于“企业家”一词的模糊而产生的幻想?其实,的确有超过10亿人在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或公司,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才华、技能或是必要的风险承受能力。小额信贷及其他有助于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仍然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这些小企业要存活下去。或许,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很多穷人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们能以此铺出一条逃脱贫穷的路,那么我们简直是在自欺欺人。
如 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穷国家,一些援助怀疑论者表示,正是由于政府失职,国外援助及其他来自外界的援助才对该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该国的状况更加糟糕。当今,很多政府的垮台都是因为一些好政策没能真正实施或发挥作用。
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乌干达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包括维修教室、购买课本以及学生学习期间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教师的工资甚至直接被计划在政府的预算之内。1996年,李特瓦·雷尼卡和雅各布·斯文松试图弄清楚,由政府分拨的这些辅助资金究竟有多少真正被用到了学校。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他们派遣调查小组到学校,询问学校负责人实际接收的资金数目,然后将这些数字与电脑里记录的政府实际派发的数字比对,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学校只拿到了实际援助资金的13%,有一半多的学校甚至没有拿到这笔资金。调查表明,大部分资金最终都到了政府官员的口袋里。
同样的结果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证实,这样的结果无疑使我们很失望。我们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为此烦恼呢?威廉·伊斯特利,一位曾经批评随机对照实验的人士,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写道:随机对照实验对于处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大问题根本行不通,诸如好的体系或是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大范围经济效应等。他甚至推断,信奉随机对照实验会削弱发展研究者的进取心。
这一观点很好地反映出一种制度化观点,并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中盛行。该观点认为,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找到良好的政策:这是一个如何挑选出恰当政治程序的问题。如果政治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好的政策便会随之出现;反之,没有好的政治导向,就无法指定或实施好的政策,至少从规模上来讲是这样的。如果1美元中的87美分都无法真正进入学校的账户,那么就没有必要弄清楚学校会如何利用这1美元。随之而来的是“大问题”需要用“大办法”来解决的社会改革,如过渡到有效民主。
而另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则认为腐败是一种“贫穷陷阱”,这并不奇怪。贫穷会引起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对此,萨克斯给出的建议是,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变富来拆除这一陷阱。这种援助可以用于实现一些特殊目标,例如疟疾控制、食品生产、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等一些容易衡量的指标。此外,萨克斯还认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有助于政府和民间团体遵守法律法规。
根据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的数据显示,乌干达政府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8个国家级地区中,排名第143位(排名高于与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尼日利亚、尼加拉瓜、叙利亚,次于厄立特里亚国)。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落后腐败的国家大规模实施反腐败计划。在乌干达政府的腐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对乌干达教育的援助不可能取得成效。
然而,雷尼卡和斯文松的故事却是以奇妙的结局收尾的。当他们的调查结果在乌干达公布后,曾一度引起骚动。而财政部得知此结果后,开始将每个月下发给学校的资金数目公布在乌干达主流媒体上。2001年,雷尼卡和斯文松再次对学校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80%的拨款都到了学校。大约有一半的学校校长曾经抱怨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拨款,最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拿到了拨款。并且,没有报道称有人对这些学校的校长或是对此事做出报道的媒体进行报复。如今看来,似乎因为无人担心公款的去向,才导致滥用公款现象的发生。这样一来,在无人监管时,地方官员便可能会轻易盗用公款,但是当监管有力时,他们则会停止这种行为。
乌干达的校长们大胆推断:如果偏远地区学校校长能够在有利政策落实之前避免腐败,那么或许我们无须等待政府的彻底改革或是社会转型,通过缜密思考和严格评估就能帮我们制定出制止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相信这些不断的进步和无数细小变化的积累,最终会导致彻底的变革。
腐败或是玩忽职守,都会造成大量的效率低下。试想一下,假如老师或护士都不去工作,那么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政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假如卡车司机通过行贿超载运输,那么政府部门就需花上数十亿美元来维修因为卡车超载而造成的路面损坏。
我们的同事德隆·阿西莫格鲁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如今都活跃在经济领域。当时,他们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认为只有当制度稳定下来后,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但是,制度却很难稳定下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曾经这样定义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诱因,这些诱因会对教育、储蓄、投资、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等产生激励作用。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对官员的约束能力。”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思考制度的建立的。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就像财产权利或税收系统,政治制度就像民主或专制、权力集中或分散、普选制或有限制的选举权。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一书中,大部分经济政治学者一致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良好的经济制度将鼓励公民投资、积累并发展新技术,因为这些是促进社会繁荣的因素。反之,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产生负面效果。问题之一就是,统治者有构建经济制度的权力,他们无须考虑公民的利益或公民的生活是否能提高。他们构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制度,制定大量限制条件,规定每个人的职责,从而削弱竞争,稳固其政治地位。这也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所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领导者建立为自己牟私利的经济制度。当政治制度运行良好时,它就能通过向统治者施加足够的限制,来确保他们不会与公众的利益背离太远。
不幸的是,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当政的领导者倾向于制定能够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政策,而他们一旦变富,又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提前阻止可能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
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述,阴魂不散的腐败制度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的领导者继承了殖民地时期该国统治者的一些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不是为大众服务的,而是为统治者谋取最大利益的。摆脱殖民主义后,新统治者发现,这些旧制度能够帮助他们很方便地谋取自身的利益,于是他们保留了这些政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所写的一篇经典文章曾提到:殖民主义时期,腐败制度阻止了欧洲殖民者的进一步扩张,建立更糟糕的制度(因为他们的扩张是从离自己国家较远的地方攫取资源并加以利用的),而这些制度在殖民主义结束后却被延续了下来。
阿比吉特和拉克希米·耶尔在印度找到了腐败制度长期残留的例子。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土地税收制度(这主要由当时任职于那一地区的英国公务员的思想意识,以及当时英国统治之下流行的言论而定)。在土地管辖制度下,印度地主负责征收土地税,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势力,稳固了封建制度。而在土地税收制度下,农民自己负责自己的土地税。这些地区的人们之间形成了合作和平等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与那些由村民统治的地区相比,由上层人士统治的地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农业产量低,学校和医院数量少。150年甚至更久以后,土地税收制度才最终被取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之前的殖民主义者也有可能摆脱糟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这需要有适当的武装力量和一定的机遇。他们特别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大革命都是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不受欢迎的动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此书的结尾讲述了如何能够改变上述状况,但是他们的态度非常谨慎。
此后,又有两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产生。这两种观点是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却不像二人的观点那么悲观。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糟糕的制度阻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依靠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力量来摆脱窘境,如果有必要,富裕国家可以采取武力。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试图操纵一个制度严密的国家的制度或政治的做法,都将失败,改变只能依靠内部力量。
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或许能打破这种糟糕制度的恶性循环。在新增长理论领域赫赫有名的保罗·罗默,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如果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国家,那么就将其委托给能够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尽管如此,管理整个国家仍然很困难。所以,你可以尝试管理一个城市,小规模的城市更便于管理,你可以对这个城市做出很大的改变。保罗·罗默受香港成功发展的激励(香港曾经由英国管辖,后归还给中国),提出了“特许城市”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把一个近似“空白”的领域交给另一国家管理,后者则负责在这一领域建立完善的制度。刚开始时,它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之后有可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拥堵费、电力的边际消费,当然也包括对产权的合法保护)。因为每个来到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自愿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区域,所以他们对这些制度不应该有抱怨。
这一设想有个小小的缺点,即我们不太确定贫穷国家的领导者是否愿意加入。进一步而言,即使这些领导者加入了,他们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尚不确定——没人敢保证:交出去的地区发展好了之后会送回。于是一些发展专家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保罗·科利尔(牛津大学教授和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在其著作《最底层的十亿人:最贫穷的国家为何继续衰败?》(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及《战争、枪炮和选举:危险地区的民主》(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中称,世界上现在有60个处于无助之中的国家(乍得、刚果等),那里生活着10亿人。这些国家都被糟糕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它们从中解脱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干涉。他认为这方面的一个成功例子,就是英国政府帮助羽翼未丰的塞拉利昂实现了民主。
然而,威廉·伊斯特利对于塞拉利昂的例子却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伊斯特利指出,接管一个国家远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美国花费了沉重的代价才在伊拉克构建了完善的体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通常来说,一种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色,因此,任何照搬式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有可能,所有的改革都必须逐步进行,要知道,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
总之,伊斯特利对于外界专家的怀疑不仅针对外来管理者,还包括外界援助。从某种程度而言,外界的援助都在试图改变原有的政策,但是这种改变通常是以破坏原有政策为代价的,即使领导人已开始腐败,他们仍然在接受援助。
然而,伊斯特利对此并不悲观。他指出,每个政府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他们自己单独完成。尽管伊斯特利对外界援助者心存反感,也声称一种制度不能适合所有国家,但他指出,自由是唯一可行的万能策略。自由意味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在人类的种种发明之中,自由市场的能量被大大低估。他主张“让70亿专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市场让所有创业者都有机会创业,如果成功了便能创造财富。伊斯特利还进一步指出,应该让民众自行决定自己受教育的程度和医疗方面的状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干预。
当然,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完全自由的市场并不是理想的结果。首先,正如伊斯特利指出的那样,穷人无法真正参与到自由市场中去。”在他们参与进来之前,他们都需要帮助。其次,社会和市场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来发挥其功能。例如,一个人不会开车,可他仍然想开。但是社会规则不允许他开车,因为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很显然,在开车需要有驾照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市场自由化。如果一个国家呈现弱势或是腐败的态势,那么自由市场也会以行贿或腐败的方式出现。一项调查显示,在德里,如果你掌握了驾驶技术,你不一定能拿到驾照;但是如果你愿意行贿,你很快就能拿到驾照。德里驾照的这种随意颁发,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当避免市场的随意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后,如何才能让政府发挥作用。这也恰恰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政府有必要为人民提供日常的必需品,而且还要制定某些政策,发挥市场的功能。伊斯特利还指出,民主能够给政府提供直接的反馈信息,约束政府履行其职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构建自由市场机制和民主。伊斯特利一贯主张,自由不能从外部引入,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此,这些制度必须是从本土自下而上形成的。最终,我们要为个人的平等和权利而奋斗。
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糟糕的制度非常“顽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将其消除。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如下结论所持的怀疑态度,即从外界引入一个制度会对原本的制度构成威胁,以及如果让人们自行处理,最终他们有可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制度。但是,如果把上述两种结论分开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事实上,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已看到了一些制度的部分变革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大变革。
事实上,我们都错失了制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准则。这一概念包括了以往分析中的大部分概念,它们通常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主导,如民主、地方分权、产权、等级制度等。但是这一层面的制度是可以通过当地一些具体的“制度”来实现的。例如,产权制度就涵盖了一系列的法规,规定谁能拥有什么(瑞士政府规定,外籍人士不能购买当地的小木屋),所有权是什么(在瑞典,人们拥有在任何地方行走的权利,包括在其他私人的土地上),如何将立法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实施这些政策(陪审团审案在美国很普遍,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却行不通)等。民主政策规定了谁能参选什么样的职位,谁能投票,如何竞选,但是法律保护有时却使得拉选票或欺骗民众变得轻而易举。就此而言,即使是专制体制,有时也会给民众保留一点儿参与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详细介绍过,制度也不例外。归根结底,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做一个转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悲观态度来源于,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激烈的政体改革——从一个专制腐败的政体转变为一个功能完善的民主政体。从底层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要增强职责和减少腐败,我们不一定要对政体进行彻底的改革。
尽管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少之又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发现民主在地方一级被一定程度地引入。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就曾发生过,例如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尼、军队独裁制下的巴西、革命制度党时期的墨西哥。近些年,推行地方选举制度的国家也有很多,1998年越南推行这一制度,也门在2001年、沙特阿拉伯在2005年也推行了这一制度。这些选举制度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选举通常有舞弊现象,而且选举人的权利很有限。然而,即使是毫不完善的地方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管理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地区逐步推行了村级选举制度。早先,中国共产党赋予村民参加选举的权利。共产党党支部任命党支部书记继续在村级行使领导权。投票不是采取匿名选举方式,投票箱经常都被塞得满满的。尽管这种选举制度不无瑕疵,但是调查却显示,选举制度改革产生了惊人的作用——村政府对村民更加负责。村里开始选举的时候,村级干部放宽了一些不受村民欢迎的政策。在中国农村,土地经常被重新划分,而一些中等收入的农户从中受益颇多。公共支出也大多被用在了村民的需求上。
同样,即使没有固定的、大的反腐体系,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还是有可能的。政府的直接干预很有成效,乌干达政府很好地利用了新闻战,收到了成效。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印度尼西亚,腐败现象在总统苏哈托下台后依然很严重。2010年,在全球腐败透明指数所涉及的178个国家中,该国排名110。在由世界银行出资、帮助当地边远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的政府项目上,腐败现象尤为明显。对于当地官员而言,多开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发票金额是最简单的腐败方式,但是他们没有采用。我们的同事本杰明·奥肯雇用了一个工程队,在大约600个村子里挖开一段道路,从而计算出究竟有多少材料被用在了道路上,然后再与原来上报的费用做比较。另外一组人则通过采访村中当时参加施工的工人,调查他们到底拿到了多少工资。结果发现,上报的工人工资的27%和原材料费用的20%都不知所踪了。更糟糕的是,这只是腐败的一部分。建好的道路长度和要求的一样长(否则,他们的腐败行为就太明显了),但是原材料的不足使得道路的质量特别糟糕——在下雨时很容易就被雨水冲毁了。
在反腐败方面,负责修建项目的政府官员告知村级领导人,他们修建的项目要经过审计,审计结果将会公布给群众。然而,政府的审计人员并不是很公正,他们毕竟还在现存的体系内工作。尽管如此,奥肯指出,与没有审计人员介入时相比,其腐败的数额还是减少了1/3(审计核查都是随机抽查)。
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我们和警察局联合向当地警察部门“虚报”一些小的犯罪行为,例如偷手机、在街上骚扰妇女等,试图让当地警务人员对这些予以备案。结果,在我们第一批上报的“案子”中,只有40%得到备案。这是因为印度警察局工作的评估是以没有办理的案件的数量为依据的,没有办理的案件越多,评估的结果就越差。因此,要想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他们就得尽量少对案件进行登记备案。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穷人很少为一些小麻烦去警察局报案。
印度的警察局几乎完全延续了其殖民时期的风格。尽管警察局设立之初是为保护殖民者的利益的,但是印度在独立后,却一直没有对其进行改革。1861年通过的警察局法案一直被沿用至今。自1977年以来,很多改革委员会都推出了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实施。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每个虚假报案者即将结束叙述、要被备案时,警察们都能找到其中的疏漏之处,进而四处奔走,寻找线索,尽快破案,以减少备案记录。尽管虚假报案者的信息不会被他们的领导知道,虚假报案者也不会因此被制裁,但是报案登记率还是从第一次报案的40%上升到了第四次报案的70%。警察对这些虚假报案者无从查起(他们都是由当地居民联合起来编造的虚假报案者),在这种情况下,登记率自然会提高。因为担心虚假报案者的再次出现,警察们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严格的监管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想法,但是审计和对虚假报案者的处理似乎有效,因为一旦消息外泄,那么触犯者就会被处罚。只要体系内的少数人相信这一点,那么对反腐败还是有用的。
由南丹·奈尔卡尼提出的信息科技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上述腐败问题。他过去曾管理过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印度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印度一直致力于给每位公民提供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这个号码和他本人的指纹以及眼睛的虹膜识别相匹配。这一概念就是通过这些识别设备来随时随地确认人们的身份的。一旦这一理念得以实现,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指纹扫描从政府部门买到由政府补贴价格的粮食。这样就可以避免粮店的老板将粮食以高价卖给穷人。尽管印度政府体系的弊端仍然存在,但是这一“科技手段”的实施却能很好地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尽管我们还无法证明这点,因为这一科技体系仍在建立过程中)。
即使在糟糕的制度框架内,社会责任和反腐败仍有提升的空间。相反,良好的制度却未必能得到真正落实。而且,这还取决于制度中有多少成分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悲观主义者认为好的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至关重要。然而,那些看似微妙的小变动给最终结果带来的影响也同样没有得到认可。
在巴西,我们发现了由于制度中的小变动对结果产生的巨大影响。先前,巴西一直沿用比较复杂的纸质投票制度。投票者需要从一长串的候选人名字中选出一个名字,并将该名字(或序号)写在投票纸上。在全国有大约1/4的成人未受过教育,这实际上剥夺了大部分人投票的权利。在普通的选举中,将近1/4的投票无效或不被计算在内。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子投票制度率先被引入一些大城市,而后相继被引入其他城市。投票者可以通过电子显示屏看到候选人的照片,并在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选择候选人的号码,完成投票。改革的最初目的是要更好地统计投票数目,但是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引入这种电子选举制度的城市,其投票结果中的无效票数比未引入的城市要低11%。新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大都比较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将票投给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候选人。此外,他们还将票投给施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候选人。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增加使得贫困妈妈生育的低体重新生儿数量减少。没有明显的政治冲突,仅仅通过一个小小的科技方面的改变,巴西穷人的意见就被纳入了巴西政体。
此外,地方政策的变化也会给政权带来一定的改变。大多数国际体系现在奉行的新理念都是将责任转嫁给受惠者,让他们负责学校、医院以及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当然,通常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征得受惠者的同意,就将责任转嫁给了他们。
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当政府无法通过公共服务的福利让群众受益时,再次实施反贫困政策则是很有必要的。当受惠者由于糟糕的服务而无法得到实惠时,政府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这些受惠者掌握着大量的信息,他们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应赋予受惠者监管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权利(老师、工程师、医生),让受惠者有权利雇用或解聘他们,或者至少有权利投诉这些服务提供者,从而确保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是正确的。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社会服务造成风险者,社会应对其加以控制。”此外,在内战结束后,社区可以通过集中组织一些集体公益项目来增强与公众的联系。在塞拉利昂、卢旺达、利比亚以及印尼这样有军队冲突的国家,由社区选择和实施的集体项目(即社区驱动发展项目)是非常受欢迎的。
然而,在现实中,社区参与以及非集权化很普遍,但社区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群众的利益呢?如何才能保证弱势群体(女人、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低下者、无房产者)的利益呢?
在上述环境下,决议的公平性以及结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一些细节,例如项目选择规则(一次会议、一次投票),谁被邀请参加会议,谁发言,谁负责监管项目的实施以及这些项目领导者是如何挑选的等。如果规则将少数民族和穷人排除在外,那么我们不知道是这种非集权化还是将权利赋予地方更有助于维持公共和谐。毕竟,被自己的邻居剥夺了公民权将令人愤怒。
以村级会议为例,这是地方重要的政治体系。通过会议,人们发泄不满、表决预算、提出或通过一些项目。村级会议可能是由充满奇幻色彩的美国佛蒙特州的年度城镇会议而来,该会议总是充满温和而又机智的幽默。但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会议却不受欢迎。例如,在印尼召开的KDP发展项目会议(世界银行给当地的社区出资修复当地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或灌溉系统)。在村里几百个成人中,有55人参加,其中一半是村中的上层人物。然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不发言。在KDP会议上,平均发言人数只有8人,其中有7人是上层人物。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寡头政治铁律”在村级政府卷土重来。但在将其中的规则略微做些改变后,结果大不一样。在印尼的一些随机挑选的村子里,政府通过信函正式邀请村民参加会议。结果,出席会议的平均人数增加到65人,而且有38人不是来自上层社会。会议中,很多村民都发言了,这使得会议很有气氛。此外,政府还将印有“对KDP会议的建议”的表格附在邀请信内,随机在印尼的一些村庄发放,由学生将此信函带回家,而剩余的村庄则由村长负责发放这些邀请函。结果,由学校发放的那些评价表格所反馈的信息比通过村级政府发放的评价表格得到的反馈信息尖锐得多。
如果规则的不同会产生巨大的差别,那么由谁来制定规则就很重要了。如果乡村实行自行管理制度,那么规则就只能由上层人物来制定。这时,如果当权者能够考虑到少数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由他们来做决策是最好的方式。将权利赋予人民,但不是所有的权利。
严格规定代表的限制条件就是由上级监管下级干涉制度的典型例子。这些限制条件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准确地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这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印度的村级政府部门(即村委会)对于代表就有这样的限制条件。村级政府部门每5年会选举一届新的领导人,同时对一些集体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建筑、道路等)重新招标。为了保护未被充分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规则中特意为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包括社会地位低的人群)保留了领导职位。如果上层人物占据了整个村委会的职务,那么,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利益将难以得到保障。村委会的真正当权者始终在管理整个村子,一旦被限制,他们就可能委托他们的妻子或是比他们地位低的仆人出面,行使自己的权力。事实上,2000年,拉加本德拉·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做了一项关于村委会制度的调查。他们想确认是否应委派女领导者担任各项基础设施的负责人。结果,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么做是无用功,这些人大到加尔各答乡村发展部长,小到他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很多当地的学者)。大家都说,村里的所有项目事实上都是由村长——男性负责的。而那些害羞的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决定,她们总是听从男人的。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孟加拉国,根据配额制度的规定,每隔5年,1/3的村委会领导都是从妇女中随机选取的。在这些村庄中,只有妇女才有权力管理村委会。仅仅在配额制度实施两年以后,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便对有配额制度的村庄和没有的村庄做了对比调查。在孟加拉国,那些由妇女领导的村庄,她们将政府的预算大部分都用在了受妇女欢迎的基础设施上——道路和饮用水等(很少一部分用在学校)。随后,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又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得到了相同的答案,拉贾斯坦是印度有名的以男人为主的地区。结果发现,这里的女人更注重水资源,而男人则认为道路最重要。因此,毫无疑问,女领导者将更多预算投在了水资源上而不是道路上。
印度其他地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几乎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拥有相同预算的前提下,女性似乎比男性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受贿的概率更小。然而,每当我们在印度公布这些研究结果时,总会有人告诉我们,这肯定是错误的。这些人曾亲自去过一个村庄,并和一个女人谈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都处于丈夫的监视下。他们还见过这样的政治海报,上面照片中候选人的丈夫比候选人本身更显眼。其实,我们也有过类似的谈话经历,也见过那样的海报。让女性参选政治领导者,这种变革有时会事与愿违,强势的女性会夺权并对其村庄进行改革。村民们认为,当选的女性领导者常常与有政治背景的人有关系,她们不太可能主持村级会议,也很少发言。她们所受的教育更少,从政经验也不多。然而,尽管她们要面对这种明显的偏见,很多女性正在逐步走上领导者之路。
最后一个例子是种族划分在选举中的角色。我们认为,选举常常基于种族忠诚度,也就是来自最大种族的候选人常常会当选,无论他本身具有怎样的品质。
伦纳德是纽约大学政治科学家,曾是贝宁地区的学生领袖。为了测量种族偏见的政治优势,他来到总统大选候选人召开政治会议的地方,说服他们到不同的村庄做不同的演讲。在一些渴望被“庇护”的村庄中,候选人强调的是种族背景,然后承诺为该地区的本族人建设更多的学校及医院,创造更多的政府工作岗位。在一些推崇“国家团结”的村庄中,这位候选人会承诺致力于国家在医疗及教育领域的改革,并致力于促进贝宁地区所有民族的团结。这些收听不同演讲的村庄都是随机选取的,但所有村庄都属于该候选人的政治根据地。“庇护”式演讲显然赢得了胜利——平均来看,“庇护”式演讲使候选人得到了80%的选票,而崇尚“国家团结”的村庄仅为他投了70%的选票。
出于各种原因,种族政治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选民们的选择基于种族而不是政绩,代表大多数群体的候选人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候选人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因为他们来自“正确的”阶级或种族,这就足以保证他们会中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北方邦越来越倾向于阶级论,这就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阶级群体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赢得选举的政治家们都出现了更多的腐败现象。至于统治某一地区的是上层阶级还是底层阶级,这并不重要,但来自统治阶级的领导者更有可能腐败。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立法议会中有1/4的成员都与刑事案件有所牵连。
在发展中国家,难道选举也会不可避免地由种族主导吗?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种族忠诚度是传统社会的基础,而且注定会统治政治态度,一直到该社会变得现代化才会有所改变。然而,证据表明,种族选举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稳固。2007年大选时,阿比吉特、唐纳德·格林、珍妮弗·格林及罗西尼·潘德在北方邦展开了一项实验,他们与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了一次非党派活动。在随机选择的村庄中,人们听到这样一句口号:“不要基于种姓来投票,要为发展而投票!”这一简单的信息将选民们为本种姓候选人投票的概率从25%降至18%。
为什么有些人根据阶级投出选票,而当一家非政府组织让他们再考虑一下时,他们就会欣然改变自己的主意呢?一个答案是,选民们对他们将要做出的决定常常缺乏了解——除了在选举时期,他们一般都没见过候选人。选举时,每个候选者都会做出类似的承诺。他们无法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机制,来发现哪些人腐败,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会腐败。而且,选民们对于立法者的实际权力也知之甚少。在印度,我们常常听到,市民们责怪立法者无视贫民区的下水道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应由地方立法者来负责。结果,立法者们认为,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受到责怪,这更加不利于一种强有力的执行机制的产生。
在选民们看来,所有候选人都大同小异(或者都不怎么样),所以他们或许觉得,最好还是依据阶级而投票:这种效忠于阶级的行为得到回报的概率很小,政治家也不太可能会向他们提供帮助。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此外,很多人并不在意选举,所以他们才这么容易改弦易辙。
巴西曾努力向选民们提供关于候选人的有用信息。自2003年,随机选择的60位市政官员每个月都会参加一次电视“抽奖”,他们的账户会受到审查。审查结果会通过网络及当地媒体公之于众。这种审查会减少腐败现象。在2004年的选举中,如果候选人的账户审查结果被公布,他们当选的概率就会减少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诚实的候选人来说,如果他们的账户审查结果在大选之前公布,那么他们当选的概率会增加13个百分点。在德里贫民窟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如果选民们得知候选人的表现不佳,他们就不会将选票投给他。
因此,政治与政策并无多大差别,其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微小的干预似乎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倡的理念——注意细节、了解人们怎样做出决定、怎样配合实验——也同样适用于政治。
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享有优先于经济的地位:经济政策的范围会据此受到界定与限制。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监管力度较大的环境中,机构功能的改进并不彻底。很明显,并非所有问题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巴西政治家们的账户并没有依据法律而被曝光,德里的报纸也不会刊登立法者的记录。在印尼,其政权本身也不反对民主制。重要的是,如何寻找这一突破口。就政策来说也是一样,政策并非完全由政治所决定。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会有好的政策产生。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环境中,常常会产生恶劣的政策。
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哈多是一个独裁者,尤以腐败著称。每当他生重病时,他的亲戚所拥有的股票的价值就会下跌。这表明,与他建立联系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苏哈多时代,用来买石油的钱被用来建学校,因为苏哈多认为,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力方式。他统一了全国的语言,在民众中建立了一种团结感。我们曾报道过,这种政策促进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受益于学校教育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工资也会增加。伴随着教育的发展,一个提高儿童营养的大计划产生了,内容涉及训练100万名村庄志愿者,让他们将这一信息带回村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干预措施,1973—1993年期间,印尼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减少了一半。这并不是说,苏哈多政权对于印尼穷人来说有多好,而是强调政治精英的动机有多复杂,他们或许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特定地点,出于自身的利益才出台这些政策的,而这些政策恰巧是有利于穷人的。
同样,相反的情况也会成立。良好的意愿对于良好的政策来说,或许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糟糕的政策也出于良好的意愿,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所在:公立学校体系令大多数人失望,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只有精英才能学习。穷人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存钱,因为对于那些允许穷人存款的机构来说,政府为他们设定的管理标准非常高。
部分问题在于,即使政府的用意很好,他们却很难做出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自由市场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干预才有必要出现。例如,很多家长可能最终没有为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也没有给他们服用驱虫片,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对于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家长可能没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接受正确级别的教育,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清楚孩子长大后是否能够回报他们;公司不愿进行废水处理,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做的费用很高,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水污染的问题;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宁愿闯红灯也不愿停下脚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政府的代理人(官僚、污染检察员、警察、医生)无法因为其他人带来价值而得到回报——当警察给我们开罚单时,我们会抱怨,但我们不会因为他敬业、维护道路安全而嘉奖他。相比之下,杂货店主通过向我们出售鸡蛋而传递价值,当我们向他付钱时,我们知道自己支付的是他所产生的社会价值。
这一现象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我们很难对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进行评估,这也是为什么公务员(警察、审判员等)有很多规定要遵循。第二,破坏规定的诱惑力总是存在的,无论公务员还是我们都是一样,这常常会导致腐败及渎职现象的发生。
因此,腐败和渎职的危险在任何政府都是在所难免的,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尤为严重:第一,政府要求人民做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例如骑摩托车时戴头盔或是给儿童接种疫苗。第二,当人们得到的价值大大高于他们所付出的时,例如医院免费提供床位给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的收入高低与否,这就导致更富有的人行贿插队。第三,官僚的收入较低、工作量较大、监管不力,而且即使被解雇也毫无损失。
前面几个章节中的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在贫穷国家可能更为严重。由于缺少正确的信息以及政府长久以来的失败,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少。极度贫穷使很多服务需要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馈赠。而且,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到底有哪些,也无法有效地要求或监督政府的表现、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有限资源等。
这也是政府计划(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发起的类似计划)常常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一直都难以解决,细节方面需要大量关注。这种失败常常并非像很多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由某一特定团体的破坏而引起,而是由于整个体系的构想都很糟糕,而且没有人愿意对其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就意味着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有效的,并且担负起责任来。
医疗工作者的缺席正是这样一个例子。您或许还记得第三章中说到的,乌代布尔地区的护士很不欢迎我们,因为我们的计划增加了她们的工作量。结果,她们笑到了最后:我们与非政府组织赛娃曼迪及当地政府展开的这一计划最终失败了。
在这一计划启动之前,我们对在赛娃曼迪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研究。数据显示,护士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缺勤的。地区行政长官决定,要加强执行护士出勤率的规定。根据新的方案,大多数护士每周一都要在中心待一整天。在这一天里,她不许外出对病人进行探视(这常常是不去上班的一个好借口)。赛娃曼迪负责监测出勤率:在每周一,每个护士都会得到一个印有时间、日期的邮票,然后多次填写贴到中心墙上的签到表上,以此证明她出勤了。至于那些出勤率不到50%的护士,她们会被扣工资。
为了验证我们的做法是否有效,我们派出了独立的调查人员,对赛娃曼迪监督的地区及其他地区护士的出勤率进行调查。一开始,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该计划实施前,护士在岗率为30%左右,到2006年8月,赛娃曼迪监督地区的护士在岗率上升至60%,而其他地区的这一比率没有变化。每个人(除了护士,因为她们见到我们时就告诉了我们)都很振奋。到2006年11月,情况开始逆转。监督地区的护士在岗率开始下降,并且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4月,受到监督的地区与没受到监督的地区,其情况都同样糟糕。
当我们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时,惊奇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该计划结束之后,记录中护士的出勤率仍然很低。记录中出现最多的是“事假”——护士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理由,例如培训和会议是最为常见的。我们试着弄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事假日突然涌现;在她们所说的日期,我们并没有发现会议或培训的记录。唯一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监测中心里,当护士突然多申请30%的事假时,每一个负责监督护士的人都决定睁一眼闭一眼。最终,她们发现,自己的上司根本不关心她们是否来上班,因此她们认为自己的实际出勤率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没有监测的中心相比,监测中心的护士出勤率其实更低,而且直到研究结束时依然如此。最终,监测中心护士的出勤率只有25%,没有人抱怨。对于中心没人工作的情况,村民们已经习惯了,因此他们对整个制度都失去了兴趣。在我们对村庄的拜访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抱怨护士缺勤的人。每个人都完全放弃了这项制度,认为不值得去弄清楚护士们在做什么,更不用说要抱怨了。
妮丽玛·科顿是塞娃曼迪的主管,她对这一情况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科顿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她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了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并希望其他人也能照做。但这些护士却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她们对于自己的玩忽职守似乎很不以为然。她还发现,她们需要做的事情十分令人震惊:一周工作6天。签到,然后拿上你的药箱,出发前往一个小村子巡诊,即使在38度左右的天气也是如此。她们挨家挨户地为育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做检查,还要劝说少数对此毫无兴趣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在五六个小时的工作之后,还要走回中心做下班登记,然后乘2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
很明显,没有人能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下去。人们对此十分理解,他们并不指望护士能真正完成所规定的工作。那么护士实际上应该做些什么呢?她们应该有自己的规则。在我们见到她们时,她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指望她们能在上午10点之前来上班,而清晰地贴在中心外面墙上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
显然,这些规定的设立并不是要降低印度整个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相反,这或许是由一位善意的官僚提出来的,他对这个体系该做些什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过多关注那些被要求实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问题:意识形态、无知和惯性。这个问题瓦解着可以帮助穷人的各种努力。
护士的工作量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将护士看成是充满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这种意识形态出自对各种条件的无知,大多因惯性而反映在文件之中。改变这些规则,使护士的工作变得更好操作,这或许还不足以提高护士的出勤率,但仍然是必要的一步。
这三大问题同样使印度家长和学生承担教育和被教育责任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印度政府在最近的一次教育改革中,引入了父母参与监管子女小学教育的观点。SSA是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大型项目,由联邦政府资助,每个村庄都要成立一个村庄教育委员会(或称VEC,相当于美国的家长–教师协会),协助学校进行管理,寻找改进教学质量的方法,并对出现的任何问题进行汇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庄教育委员会可以为学校增加一名教师而申请资金,如果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委员会有权雇用或者根据需要解雇这名教师。考虑到雇用教师的成本不低,这可以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决策。然而,根据我们在北方邦(印度人口最多的一个邦)江布尔区所做的调查,在这一计划制订近5年之后,我们发现92%的家长从未听说过村庄教育委员会。此外,在我们对该委员会成员的家长进行采访时,1/4的人都说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约2/3的人并不了解SSA计划,也不知道其拥有雇用教师的权力。
这一计划同样受到了这三大问题的阻碍。在“人民的力量很大”这种意识形态的启发下,这一计划完全忽视了想要什么及某一村庄如何运作。在我们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时,它完全是由惯性支撑着。很多年以来,根本没人注意过这个计划,除非是某地的官僚,因为他需要确保所有的意见箱都已检查过了。
Pratham是印度一家教育非政府机构,负责年度国家教育报告,还有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的有关教育的阅读计划。通过与该机构的共同研究,我们认为,让父母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可以为计划注入新的活力。根据SSA计划,Pratham小组派出实地考察员到65个随机选择的村庄,告知那里的父母们他们拥有哪些权利。Pratham小组有些怀疑,如果只是告诉人们他们能做些什么,而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在另外65个村庄一组中,Pratham小组教感兴趣的村民怎样使用dipstick阅读软件,还有些数学测试(这些都是ASER 的核心内容),并为该村庄准备一张成绩单。对于这些成绩单的讨论(表明在大多数村庄,具有读写能力孩子的人数少得可怜)只是一个起点,随之而来的是讨论家长及村庄教育委员会的潜在作用。
然而,在一年之后,在家长参与村庄教育委员会、委员会行动主义或儿童学习(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的问题上,这些干预都没能产生任何作用,而原因并非是这一社区没有被调动起来。Pratham小组还让这一社区提供一些志愿者,接受Pratham阅读技巧的培训,然后教孩子们怎样去阅读,并负责给孩子们开设课后阅读班。志愿者们确实做到了,他们每个人都会教几个班。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这些村庄孩子们的阅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村民们得到了一项清晰、具体的任务:找到志愿者,将有需要的孩子送到辅导班。相对于劝说人们去为增加一个教师而游说政府的模糊任务,即SSA的计划,这种方式的界限或许更为清晰。在肯尼亚,一项研究给村庄教育委员会一项任务,并让他们行动起来,结果非常成功。在这项研究中,委员会得到了一笔资金,并根据要求用这笔钱雇用一名教师。在某些学校,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即密切注意这名教师的行为,并确保学校没有误用这名教师。这一计划在所有学校都得到了良好的执行,而且在学校委员会特别关注其执行情况的学校,效果更为明显。因此,父母的参与虽然必不可少,但父母们需要做的事情也需要审慎思考。
这两个例子表明,大规模的浪费及政策失败之所以会发生,常常是因为政策规划阶段的懒惰思想,而不是任何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对于有效的政策来说,有效的政治或许是必要的,或许不是。当然,这还不够。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观点,即政治总会优先于政策。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颠倒政策与政治的阶级地位。良好的政策是良好的政治的第一步吗?
选民们根据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情况,调整自己的观点,即使他们一开始时具有偏见。印度的女性政策制定者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德里的精英们仍然认为,女人不应被赋予合法的决定权,但国民们却更为支持相反的观点。在孟加拉邦西部,在从来没有女性领导者任职的政府岗位中,2008年,10%的岗位被女性占据。毫无疑问,当这些岗位为女性预留时,这一比率上升至100%。女性当选的比率从13%上升至17%。在孟买,同样的情况也在市政府代表中发生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选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孟加拉邦西部,为了衡量关于能力的偏见,村民们需要听取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所有村民听到的都是同一篇讲话,但有些人听到的是男声,而有些人听到的是女声。听完讲话之后,他们被要求对讲话质量进行评判。在从没为女性保留过席位(也从未有过女性领导者)的村庄中,男人们给予男声演讲的分数比女声演讲更高。另一方面,在曾为女性保留席位的村庄中,男人一般都更喜欢女声演讲。男人的确承认,女人有能力执行良好的政策,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于女性领导者的观念。因此,暂时为女人保留2/3席位,不仅可以增加饮用水资源,还会永久转变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角色。
良好的政策还有助于打破过低期望的恶性循环:如果政府开始执行,人们就会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政治,并给政府施压,执行更多的政策,而不会放弃选举权,也不会不加思考地将选票投给同族之人,更不会拿起武器反抗政府。
在墨西哥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到接受了社会福利计划Progresa(为穷人家庭提供现金转移,前提是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他们要去医疗中心)的村庄,对实行该计划6个月与21个月的两组村庄在2000年大选期间的选举行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在受益于Progresa计划更久的村庄,其选票偏向实行该计划的政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可能是这些家庭被该计划“收买了”,因为那时他们都受益于此,并且已经了解那些规则,而是这一计划在改善健康及教育方面非常成功,接受该计划更久的家庭,已看到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好处。因此,他们将选票投向了启动这一计划的政党。在太多选举承诺出台而又破灭的情况下,实际的成绩向选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让他们了解候选人将来可能会做些什么。
信任的缺乏可以说明,为什么温奇康(Wantchekon)在2001年贝宁的实验中发现,与吸引公众利益相比,提供具体的信息更为成功。当政客们对“公众利益”泛泛而谈时,没有人会真正相信,至少,选民们多多少少会信任一种具体的信息。如果“公众利益”的信息更加清晰一点儿,更加专注于某些具体倡议,提出一项可以让候选人在当选后为选民负责的议程,那么这种信息更容易产生影响。
伦纳德在2006年选举之前进行了一项后续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那些认真负责、致力于涉及并解释社会政策的政治家们,选民们的确会给予支持。伦纳德开始与贝宁其他民间团体领导人进行广泛的协商:“2006年选举:政策选择是什么?”分别有教育、公共卫生、管理及城市规划四个小组,还有四位专家(其中两位来自贝宁,另外两位分别来自邻国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他们提供一本政策建议的白皮书。所有国民大会的政党代表,还有各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之后,有几家政党自愿使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作为试运行的选举平台。他们将其应用于随机选择的村庄,在城镇会议上,对这些建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参与者们有机会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在对照村庄,气氛愉悦的政治会议经常召开,会上提出了一些具体信息,还有广泛而又模糊的政策提议。这一次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那些召开会议并讨论具体政策提议的村庄,并没有出现对于具体信息的支持,但参选政党的选票数和支持率都更高。
这一结果表明,可靠的信息可以劝服选民们对符合大众利益的政策投票。一旦信任建立了起来,个别政客的激励政策也会改变。他会感觉到,如果他做了一些善事,他就会受到尊敬并再次当选。很多拥有权力的人都具有多重动机——他们想受到爱戴或做善事,因为他们有同情心,也因为这可以稳固他们的地位,即使他们有腐败行为。这些人会做一些促进变革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与他们的经济目标不完全冲突。一旦政府可以证明,他正在试图实施政策并赢得人民的信任,一种更深层次的可能性就会产生。政府现在可以不再那么关注于短期成绩,不再那么热衷于不顾一切地赢得选民的认可,不再那么沉迷于冲动下的有奖问答。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规划更加有效、更有远见政策的好机会。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Progresa所展示的成功鼓励了福克斯,他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失势之后成为总统,而他并没有取消这一项目,而是将其推广到整个拉丁美洲,推广到全世界。这些项目或许起初并不像有奖问答那样吸引人,因为为了拿到钱,一个家庭可能要做些事与愿违的事情,但人们相信(不过,我们看到,或许这是错误的),制约性是“打破贫穷周期”的一个必要部分。我们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他们都认为应当将这一长远观念摆在议程的核心位置。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多西方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都极为悲观。根据他们的从政知识,他们或许会指责陈旧的农业机构,或是来自西方的罪恶——殖民统治或傀儡机构——或是一个国家所固守的文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观点都认为,糟糕的政治机构应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的贫穷负责,而且逃脱这种贫穷状态很难。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放弃的理由,其他人则希望从外部促进机制改革。
伊斯特利与萨克斯对这些论点都多少有些反感,原因有所不同。伊斯特利认为,西方的“专家们”没理由去判断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组政治机构是好是坏。萨克斯认为,糟糕的机制是贫穷国家的通病:通过专注于具体、可测量的计划,或许以某种有限的方式,甚至在一种糟糕的机制环境中,我们可以成功地消除贫穷,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更有文化,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由此,良好的机制便会随之而产生。
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政治局限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使我们很难找到解决大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改进机制及政策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认真了解每个人(穷人、公务员、纳税人、当选政客等)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及机制,避免腐败或渎职现象的发生。这些变化还在继续,并开启一场寂静的变革。
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谈论哪些国家的经济在增长,哪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这看上去没有任何用处。一些国家由经济瘫痪转变为经济奇迹,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另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模范”沦落到谷底,如科特迪瓦。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找出合理的理由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会忽然发生。
鉴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与智慧,但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女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民们在为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贫困,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
或许,到那时,人们需要长久致力于摆脱贫困。如果不幸和挫折不请自来,气愤与暴力占据上风,那么能否摆脱贫困,我们尚不可知。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可以使人们远离失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失去什么,要让国家在其所处的时代腾飞,那么这样的政策或许是关键的一步。
如果所有这些都不正确,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不再等待经济刺激,将是大势所趋。第一章中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了如何摆脱贫困,我们不能容忍浪费穷人的才干和生命。正如本书所讨论的,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见以下5个方面。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他们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该使用多少化肥,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易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在他们发现那些坚信不疑的信念是错误的之前,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如果女孩们与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并且未采取避孕措施,或农民使用两倍于正常量的农药,这些事情的后果都是严重的。例如,由于人们不确定接种疫苗有哪些好处,再加上办事拖延的习惯,导致很多孩子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公民盲目选举,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同种族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使顽固和腐败问题变得更严重。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一条普通的信息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要想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条信息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它必须是人们尚未知晓的(如“婚前禁止性行为”是人人都知道的,效果不明显);信息的发布方式必须是简单而有吸引力的(电影、电视剧、精心设计的报告单);信息的来源必须是可靠的(有趣的是,媒体看上去似乎是可靠的)。因此,当媒体发布信息称政府做得不对,政府将花费大量的成本来挽救自己的信誉。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穷人没有自来水,因此,当市政府对水进行氯化时,他们不能受益。他们买不起速溶的强化营养型麦片,因此不得不想办法确保他们及自己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营养。他们没有自动扣除功能的储蓄计划,例如退休计划或社会保障,因此要想办法存些钱。做这些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人们考虑当下或前期做出少量付出,而回报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人们拖延的习惯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穷人,更为麻烦的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着竞争激烈的小本生意,剩下的大部分人打散工,总要为找到下一份工作发愁。这说明通过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会得到很大改善——降低加铁/碘盐的生产成本,使人人都买得起;银行提供存钱容易但取钱代价会稍高的储蓄账户,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可以对银行进行补贴,以弥补其带来的成本费用;在自来水昂贵的地方提供清毒剂以做净水处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幸拥有一个账户的话)是负利息,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市场尚未健全,尽管医疗问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在一些案例中,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可以弥补市场发展的不足,例如小额信贷市场,它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利息不高,人们支付得起;又如,电子转账系统(用手机等)和个人识别系统可以在未来几年大幅削减银行成本。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这类市场的兴盛不仅需要靠自身的努力那么简单,有时需要政府的支持。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可能会产生免费赠送的产品或服务(如蚊帐或到保健中心做检查),甚至奖励人们做有利于自身的事情,虽然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各类专家都不信任这种免费发放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是从纯粹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有些夸张了。相对于收取一个固定价格来说,免费向每个人提供服务的成本常常更低。在某些情况中,这可能需要确保市场所售产品的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允许市场得以发展。例如,政府可以补贴保险费用、发放代金券,而家长则可以在任何一家学校(公里或私立)使用,或是强迫银行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账户,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些得到补贴的市场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确保其运转良好。例如,如果所有家长都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合适的学校,那么学校代金券就非常有用;否则,这可能会成为为精明的家长提供又一优势的方式。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的确,在这些国家,事情很难办成:一项关于帮助穷人的计划由于被某些人接手而失败了;教师教学散漫;建筑施工时偷工减料,车辆超载以致道路塌陷等。这些事件几乎与那些精英们的经济阴谋无关,主要是由于制定政策时出现的错误造成的,包括无知、意识形态和惯性。人们期望护士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但从没有人想过修改护士的工作职责。在印度,一位政府高官曾告诉我们,村里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优秀生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当我们问他们如何评定好坏的标准时(直到四年级才有考试),那位官员立刻转移了话题。然而,由于惰性,这些荒唐的规定目前还在生效。
如果表达正确的话,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有可能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即使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改进的空间仍是巨大的,而在不好的环境下也有一定行动的空间。只要确保每个人都被邀请来参加村庄会议,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让他们为自身的渎职而担负起责任,对各个阶层的政治家进行监督,并将这一信息与选民分享,向公共服务用户们说明他们应期待什么——医疗保健中心的准确工作时间,他们应当拿到多少钱(或是多少袋米),那么,一次小的变革便可以实现。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他不够聪明;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护士不上班是因为没人对她们在岗位上的表现抱有期望。改变人们的期望是不容易的,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看到村里出现了女官员时,村民们不仅不再歧视女政治家,甚至开始认为自己的女儿也具备这种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善时,这种改善本身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人们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包括现金)。
除了上述5个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本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这本书旨在对这些问题抛砖引玉。如果我们拒绝懒惰和公式化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逻辑,那么我们就能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也能更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发现贫穷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我们不想做过多评论,但也不会忽略这项事业所暗藏的逻辑:小的变化可以带来大的影响。肠道寄生虫可能是你最不想提的话题,但是肯尼亚的孩子为此需要在学校接受治疗,时间长达两年,而不是一年(成本是每年每个孩子1.36美元),他们成年后平均每年多挣20%,即一个人一生多挣3 269美元。如果杀虫工作更加广泛,它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小:如果肠道寄生虫被消灭,那些孩子可能早已投入了工作。我们注意到,2006—2008年,肯尼亚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率创历史新高,为4.5%。如果我们撬动经济政策的杠杆,那么该地经济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4年内人均收入将提高20%,但是,这样的杠杆并不存在。
我们不能保证消除贫困。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获取了充足的时间。贫困已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果我们打算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那就行动起来。至少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应与全球其他人一起联手努力,让这个世界再没有人每天依靠99美分生活。
我们的母亲——妮玛拉·班纳吉和维奥莱纳·迪弗洛——在生活和工作中,曾多次表达对不公正的憎恨。假如我们当时对此装聋作哑,逃避她们的影响,我们就难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
我们的父亲——迪帕克·班纳吉和米歇尔·迪弗洛——教导我们正确讨论的重要性。我们并不能完全体会他们设定的严格标准,但我们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它是正确的标准。
这本书起源于2005年与安德烈·施莱费尔的谈话,当时他在《经济展望》杂志当编辑。他让我们写一写穷人。当我们写作最终题为“穷人的经济生活”的文章时,我们意识到,这是能将我们一生想洞察的各种迥异的事实和想法综合起来的一个方式。我们的经纪人马克斯·布罗克曼说服我们说,一定会有人对出版这样一本书感兴趣。
书中的许多信息都来自他人:他们或教过我们——指导过我们或挑战过我们,或是我们的合作者——合编者、学生和朋友,或是我们的同事,或是政府工作人员。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感谢乔希·安格里斯特、鲁克米尼·班纳吉、安妮·迪弗洛、妮丽玛·凯坦、迈克尔·克雷默、安德勒·马斯·科勒尔、埃里克·马斯金、森德希尔·莫雷森、安迪·纽曼、罗西尼·潘德、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他们以各自方式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的一些观点也被融入本书。我们希望,他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感兴趣的。
在本书写作的初期,我们从很多人的观点中受益,其中包括:丹尼尔·科恩、安格斯·德亚顿、帕斯科林·迪帕、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格雷格·刘易斯、帕特里克·麦克尼尔、罗西尼·潘德、兰·帕克、索明斯基·森古普塔、安德烈·施莱费尔和库德扎·塔卡瓦莎。埃米丽·布雷扎和多米尼克·莱格特多次通读了本书的每一章节,并提出了重要的改进建议。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本书。当然,如果我们更耐心一些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们在公共事务所的编辑克莱夫·普里德尔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书就是在他任主管时面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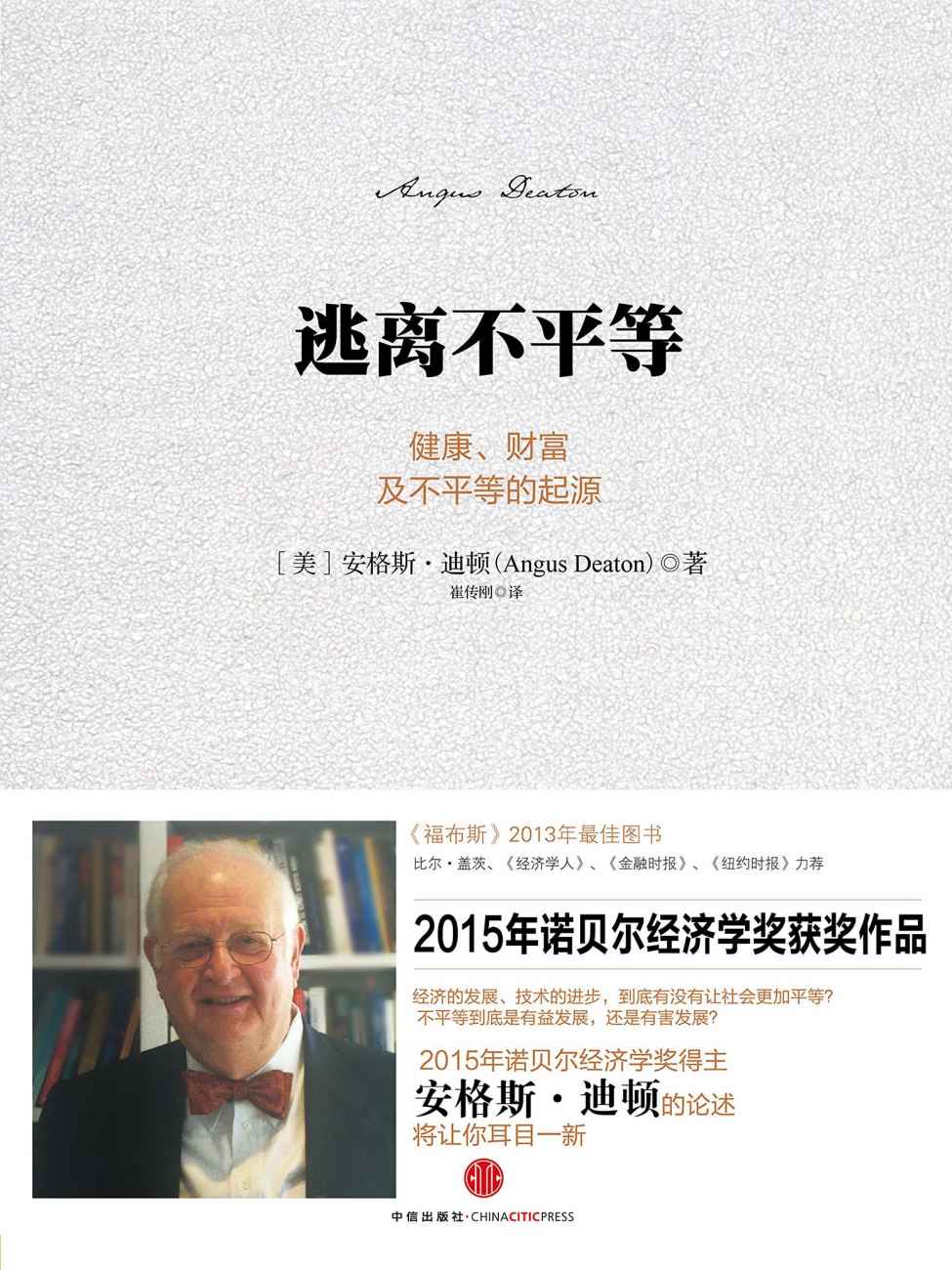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莱斯利·哈罗德·迪顿
THE GREAT ESCAPE
《福布斯》2013年度最佳图书
《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出版人协会2013年度经济散文荣誉奖
入选《金融时报》—高盛2013年度最佳商业图书榜单
比尔·盖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隆重推荐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公平、富裕的地方吗?极少有经济学家能够比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有更多的储备或资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评估衡量国际福利状况,不害怕为此追溯历史。不同于常规的研究视角,在这本书里,迪顿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叙事,关注到那些经常被忽视的领域的进步,如人类的健康改善……要驾驭这样综合的主题,需要有大的格局和大胆的构想规划,安格斯·迪顿同时具备了这两点。
——《经济学人》
迪顿这本条理清晰的书激赏由发展带来的财富,同时明晰而审慎地解释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在这样的进步中“落后”。他严格区分了由知识进步造成的不平等以及由政治系统有缺陷造成的不平等……这本书深厚的历史与地理知识背景增加了其论述的力量。
——《金融时报》
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激动人心的关于人类的寿命和繁荣程度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猛增的故事。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之后加速,经济进步和医疗技术里程碑似的发展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激增,本书便是关于这三者的一个综合阐述。
——《纽约时报》
当迪顿教授提出很多人或国家的所谓援助其实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帮助需求时,可谓一语道破真相。他识别了人们的援助幻觉——即认为通过富裕国家的人们提供资金,可以解决贫困国家人民的贫困问题。
——《金融邮报》
了解当今世界福利状况的最佳指南之一……迪顿讲述了所有人类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它将给所有人以对人类未来前景乐观的理由,只要我们愿意听取其中的道理。
——《纽约时报书评》
在这本新书中,经济学家迪顿教授质疑所有援助的有效性,同时论述了世界上更多的贫困人口是怎样并不仅仅出现在非洲,同样也出现在急速发展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中国和印度。
——《巴伦周刊》
《盛大逃亡》一书将技术的先进性、道德的紧迫感、富于经验的智慧以及一种引人入胜的写作方式做了一个惊人完美的结合。它将加深你对现代经济所取得的进步的赞赏,同时坚定你的利益能够也应该被更广泛地共享的信念。
——彭博新闻社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迪顿勾勒了一幅两百多年来人类逃离贫困和早期死亡的图景。这是一个充满能量的故事。在迪顿的笔下,所有经常被忽视的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被予以突出,这既给人以新鲜感又叫人充满期待。
——路透社
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整体福利上涨如此之多,安格斯·迪顿的这本书你将不能错过。
——比尔·盖茨
一本无与伦比的杰作。
——威廉·伊斯特利(纽约大学教授)
这本书排在我2013年必读书目的首位。迪顿处理的是一些大的话题:全球健康改善与幸福感的提高,令人担忧的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通过外国援助解决贫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他充满力量的、富于煽动性的论证结合了细致的分析、富于人文情怀的洞察、明晰的阐述以及无所畏惧的挑战传统智慧的勇气。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结论,本书都会迫使你重新思考你在一些世界最紧急问题上的位置或立场。
——克里斯托弗·伊斯格鲁布(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本书讨论了历史上两个最为重大的问题:人类是如何获得健康和财富的,以及为什么一些人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健康。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安格斯·迪顿带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凡的旅程——从几乎所有人都贫病交加的时代进入一个大多数人逃离这种罪恶的时代——同时告诉我们,那些依然陷入在这种极端贫困中的亿万人民将怎样可以加入到这场大逃亡中。所有想要了解21世纪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
没有人能够比安格斯·迪顿更好地解释为什么相比于我们的曾祖父母,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富裕。在这本书里,他不仅讲述了这一尚未完成的、未能平衡发展的势不可当的人类进步历程,同时指出了政治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任何关注国家健康与财富话题的人,这都将是一本必读书。
——达伦·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
迪顿关于全球健康进展状况的阐述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阐释经济增长方面,其论述更加让人信服,因为技术进步是健康改善的基础。这本书意义重大,它将影响我们思考人类发展的方式,同时影响我们对科学包括基于科学的政府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这本书的语言严谨优雅,其所采用的证据的说服力是不可抗拒的。
——塞缪尔·普雷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这本杰出的书所讨论的,是在过去的250年中,大量的人口是如何过上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生活水平的,以及这种进步是如何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类不平等。基于非比寻常的观点和见识、独特的知识与连贯性以及细致的论证,这本书充满了启发性,给人极为愉快的阅读体验。
——托马斯·博格(耶鲁大学教授)
深入的研究加上雄辩的论述……对于那些对世界贫困状况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发展援助的最为重要的一本书。
——肯尼斯·罗格夫(哈佛大学教授)
《大逃亡》本来是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群盟军士兵逃离德军战俘营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所说的“大逃亡”则另有所指:我要讲的是人类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希望以此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的挖煤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孩子能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39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对挪威德军的突袭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一位南苏格兰木匠的女儿结了婚。
虽然没能获得上中学的机会,父亲还是在夜校学到了实用的煤矿勘测技能。1942年,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拥有这一技能的父亲获得了青睐,成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进入公司后,父亲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于是他从头学起,之后经过10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其实读土木工程的课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两科。最近父亲曾就读的夜校,也就是现在的赫瑞瓦特大学给我寄来了他当年的考试成绩,从成绩单上也可看出,父亲当年的确费了不少劲儿。取得资格后,父亲在苏格兰边区得到了一份给排水工程师的工作,并买下了我母亲的祖母曾居住的小屋。据说早年间著名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经光顾过这座小屋。不过对我来说,爱丁堡这里只有煤尘、烟灰以及糟糕的气候。等到1955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还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父亲在这时也开始着手为我规划人生。为此,他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我的妹妹考入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做了一名教师。在我们这一辈的数十个孩子中,只有我们俩考上大学。在我俩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所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准生活,但对于他而言,他的孙辈们生活质量之高,已是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从那个煤矿小村庄的“逃亡”,是这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例证。按照今日的标准,我父亲生于贫困之境,但却终于生活相对富足。我没有关于约克郡矿区的统计数据,但是在整个英格兰,1918年的时候,每1 000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00个是活不过5岁的,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孩子的死亡率更高。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儿童活不过5岁的概率还是要高于1918年的英格兰。我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的父亲还是在年轻时被矿井里的煤车撞死了。我的外公去世时也很年轻,死因是阑尾切除感染。我父亲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患过肺结核这种堪称夺命杀手的病,但还是活到了90岁。他的曾孙子辈,我看则极有可能活到100岁。
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童年夭折的人大幅减少,人们活得更长,得以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时代的繁荣。在我的父亲出生一个世纪之后,每1 000个英国儿童5岁前的死亡数字已经降到了5个。即便在约克郡剩下的矿区中(我父亲出生地的煤矿于1991年关闭),这一数字略高,然而若同1918年相比,现在的死亡率已经微不足道。在我父亲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机会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到了我这一代,也只有不到1/10的英国孩子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了未来这件事,其实并不稀奇,但也绝非是普遍存在的。我父亲同村的人中,没几个能像他这样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我母亲的姐妹以及她们的配偶也未能如此。在苏格兰边区的铁路线停运之后,母亲的兄弟也无法再靠打各类零工来勉强度日,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举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的孩子在财务上则非常成功和有保障,他们(和我们)是极度幸运的。因为即使在现在,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和财务成功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在经受着父辈们的艰辛。我的很多朋友,子女的未来以及孙辈的教育是他们一直担忧的问题。
这是故事的另外一面。我父亲的一家得以长寿并且获得了财务成功,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人群的典型样本。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尤其明显。一少部分人大显身手,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之中。而当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旋涡中。
本书所关注的就是人类发展与随之出现的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我却想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一说到脱离贫困,人们自然会想到钱,想到如何可以有更多的钱,如何不用为钱不够花而发愁,以及如何不用担心突然的“万一”会毁掉你和你的家庭。钱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拥有更强健的体质,如何健康长寿以便能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人生,却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如同担忧金钱的匮乏一般,人也常常担忧自己的儿女不能健康长大或者要直接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母亲甚至为了保证有5个孩子能活到成年,要生育10次。纵观历史或者是当今世界,子女死亡、病痛的折磨,以及难以忍受的贫困,常常会降临到同一个家庭。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
有很多著述是谈论财富的,也有很多谈论不平等的书籍,还有很多书讨论健康问题以及健康与财富的关联: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映射。我试图把以上诸方面统一起来进行探讨,并趁此机会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闯入人口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领地。由于我们的话题事关人类的福祉,以及生命如何更有价值,因此只谈其中的任一重要部分,都难以确保详尽到位。关于人类的“大逃亡”,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学术边界的话题。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这一生欠了不少“学术债”,很多师长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理查德·斯通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为深刻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没有衡量标准,我们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亦是无比重要的事项。阿马蒂亚·森则教会我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以及应以整体的视角去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对幸福的评价,就是本书的核心。
我的朋友、同事以及学生都异常慷慨地花费精力阅读了本书全部或者部分章节。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都是无价的。我尤其要感激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他们不但给予我批评建议,同时也不吝惜赞美和肯定。同时我还要感谢托尼·阿特金森、亚当·迪顿、让·德雷兹、比尔·伊斯特利、杰夫·哈默、约翰·哈莫克、戴维·约翰斯顿、斯科特·考斯特沙克、伊莉亚娜·库泽科、戴维·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佛朗哥·泒拉奇、托马斯·博格、莱昂德罗·普拉多斯·德拉斯埃斯科苏拉、萨姆·普雷斯顿、马克斯·罗瑟、萨姆·舒赫霍弗–沃尔、亚历山德罗·塔罗齐、尼古拉斯·范德瓦尔和雷夫·温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塞思·迪奇克让我开始动笔写作此书,并在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建议。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国家老年研究所和国家经济研究局曾资助我在健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那次研究的成果对本书影响深远。我与世界银行合作频繁。世行经常要面对各种紧急与实际的问题,它教会了我如何分辨哪些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则无足轻重。近年来我一直担任盖洛普咨询公司的顾问,他们开创了对全球范围内幸福状况的调查,其中所获得的一些调查数据会出现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对以上所有的人及机构表示感谢。
最后也是最要感谢的是安妮·凯斯。在本书最初完成时她就从头到尾审读了每一个字,之后又对某些部分审读数遍。全书无数处的改进都是她的功劳,没有她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今日人类的生活水平,已近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富有,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则比以往都少。人类的寿命变得更长,做父母的也不必再承受子女早夭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经受穷困或子女早逝的折磨。这个世界变得异常不平等。
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新富们或许会利用他们的财富向政客施压,从而限制他们不需要的那一部分公共教育或者健康医疗支出。
一段时期以来,人类生活实现了何种改进?这种改进的实现过程是怎样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发展与不平等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些,是本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著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在电影中,他的角色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人真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其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屡次试图逃脱,但又屡次失败。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个战俘一起,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在电影中被称为“大逃亡”的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胜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直接下令处死。
当然,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再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这本书中,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以穷苦、匮乏、体弱多病等为表现的自由缺失,曾长期困扰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到如今,世界上仍有极高比例的人口缺失这种自由。本书将讲述人类从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中不断逃亡的故事,并详述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则是源于我对电影中那些未能逃脱的战俘的思考。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这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绝不会减少我们对逃亡本身的渴求和赞美。当我们思考逃亡的后果时,不能只考虑电影中的主角们,我们也需要留意那些被留在第三战俘营以及其他战俘营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电影里显然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怀,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人不是主角,而仅仅是故事的陪衬而已。世界上没有一部叫作“大留守”的电影。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毕竟,在德军战俘营里没能逃走的士兵,要比逃出去的多得多。另外,也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次大逃亡计划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比如,遭受惩罚或者很多优待被取消。可以预料的是,在逃跑发生之后,监狱的守卫会更加森严,未来出逃将更加不易。这些出逃行为会鼓励监狱其他人出逃吗?显然,他们可能已经从成功出逃者身上学到了出逃的技能,并且知道了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出逃的种种困难,以及出逃成功率的降低会不会打击他们出逃的念头?另外也有可能的是,对成功出逃者的嫉妒和对出逃成功率的悲观,让这些在狱犯人变得更加沮丧失望,让监狱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同其他的优秀电影一样,我们对《大逃亡》这部影片还能做出其他的解读。在电影的结尾,逃亡的成功与愉悦都消失殆尽,因为多数逃跑者得到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们又被抓了回去。人类摆脱死亡和贫困的努力始自约250年前,并一直延续至今。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的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即便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至善的事件也不例外。始于英国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至今仍未消弭的鸿沟。很大程度上,今日全球的不平等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所造成的。
不要以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其他地区就一直处于落后和极度贫困之中。早在哥伦布航海数十年前,中国就凭借足够的技术和财力,派遣一支由郑和率领的舰队前往印度洋探险。与哥伦布的小船相比,郑和的舰队简直就是航母群。比这更早300年,中国开封府就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手工业作坊烟气喷涌导致整座城市烟尘弥漫,而800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兰开夏郡的繁盛也不过如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成千上万的廉价书籍得以出版,这样即便收入低微的人也能读得起书。不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这样的时期都是不能持续的,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繁荣的起点了。宋朝曾给予金朝大量财物,让其帮助消灭自己的敌人辽国——你想让一个危险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同盟,就得给其大量的好处。但结果是,1127年,宋朝首都开封首先被金兵攻陷。在亚洲,经济增长不断启动,又不断被扼杀。扼杀经济的既有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也有战争的破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最近的250年中,世界的某些地区才开始出现长期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此种情况。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断出现差距,经济增长就此变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引擎。
工业革命与大分流算是历史上较为良性的“逃亡”了。很多时候,一国的进步发展是以其他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先于工业革命并催生了工业革命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帝国时代,这一时代让英格兰和荷兰的多数人获益良多,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成为整个过程中表现最优异的国家。至1750年,同德里、北京、巴伦西亚、佛罗伦萨等地区相比,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劳动者收入都实现了相对增长。英国工人甚至能买得起一些奢侈品,比如糖和茶叶。但是那些在亚洲、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岸被征服与被掠夺的人不但当时就受到了伤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套上了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枷锁,遭遇了持续数世纪的贫困与不公。
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不久之前仍处贫困的国家,诸如中国、印度以及韩国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经济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当期的富裕国家。从而,它们已经从较贫困国家的行列中离开,剩下的多是非洲国家,这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一些国家赶了上来,一些国家则被甩在了后面。全球化和新的发展方式使得富裕国家的财富持续增长,尽管这种增长不论是与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相比还是与它们之前的速度相比都有所下降。然而,财富增长放慢的同时,在多数国家内部,人们的财富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一少部分幸运儿赚得巨额财富,他们今日的生活方式让过去那些万人之上的帝王都自叹不如。不过,多数人所体会到的是,物质繁荣的进步程度不如以前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中,中等收入人群的富裕程度已经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当然,与更早的祖先们相比,他们的富裕程度是成倍增长了,毕竟这种物质的巨大进步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但是,今日的很多人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未来,当他们的孩子或者孙辈们回顾今天这段岁月时,是会将它视作一个久违的黄金年代,还是一个相对贫瘠的年代?
当不平等被认为是发展的侍女无关紧要时,如果我们只看到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或者更糟,只看到那些成功国家的社会发展,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业革命以前就被视为仅发生在先进国家的事,而其他国家则被完全忽略,仿佛它们在工业革命时期什么也没发生,又仿佛是那些地方自古就没有什么事发生过。这不但是对大多数人类群体的怠慢,也忽略了那些利益受损群体或者那些落后群体所做出的被动贡献。我们不能仅仅把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影响作为一种描述“发现”新世界的方式。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发展进步的平均速度也不能告诉我们发展的成果是被广泛享有了还是仅仅让一小撮最富有的人受益。前一种情况曾出现在美国“二战”后的25年中,但最近所发生的现象却属于后者。
我在本书中讲述了物质进步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既关乎发展,又关乎不平等。
同财富的增长一样,人类在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也非常值得称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0岁,并且还在以每10年增加2~3岁的速度发展。那些以前本活不过5岁的孩子,如今活到了老年阶段,而那些本可能因心脏病中年辞世的人,如今可以看着孙辈们安然长大并顺利进入大学。毫无疑问,在所有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因素中,寿命的增长属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在健康领域,进步也同样孕育了不平等。在过去的50年中,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由于受过教育,更富裕的专业人士会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条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鸿沟也就此被制造出来。在1900年左右,细菌导致疾病还是一项新知识,专业人士和受教育人群最先将这项知识转化为实践以保护自己。在20世纪的黄金岁月里,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疫苗和抗生素来保护儿童,但如今每年仍有近200万儿童死于疫苗可防治的疾病。在巴西的圣保罗或者印度的德里,富人能得到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医疗服务,而在一两英里之外,穷困的儿童却被营养不良或者一些容易预防的疾病折磨致死。健康的进步为何如此不平等?不同的情况常常有不同的解释。为何穷人更有抽烟倾向与为何有如此多儿童得不到疫苗的原因并不一样。我们会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处,我们要说的重点是:正如物质进步制造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健康的进步也制造了健康的鸿沟。
如今,“健康不平等”已成为各类重大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新的发明或者新的知识出现时,某些人首先受益,而其他人则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获益。这种不平等还属于合理,毕竟如果是为了防止健康不平等,就想要去阻止吸烟有害这样的知识传播,是非常荒谬的。重要的是这样的问题,诸如为何穷人更可能染上抽烟的嗜好,而早夭的非洲儿童,要是生在法国或者美国就能活过6岁,这种不平等为何一直存在?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本书主要关注物质生活水平和健康这两个主题。这两方面并非美好生活的全部要素,但是这两个方面本身却至关重要。在今日知识专业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学科都对人类的幸福有着自己的专门观点,把健康和物质水平两者结合起来讨论,可以让我们避开今日很常见的片面性错误。经济学者关注收入,公共健康学者关注死亡率和发病率,人口学者关注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规模。这些都是有益于增进人类幸福的研究,然而这些本身都不是在谈幸福问题。这么说的确有点老生常谈,但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却并非显而易见。
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认为,人们如果有更多的钱,就会过得更好。这观点本身有其合理性。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些人得到了更多的钱,而其他多数人即便得到很少或者没有得到,至少他们也没有受到损害,那么经济学家通常就认为,这个世界变好了。这个观点非常有号召力,并被称为帕累托法则: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那么更富有就是更好。但是这个观点如果应用在幸福问题上,并且如果幸福的定义过于狭窄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要获得幸福,生活中要变得更好的或者不应该变得更差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如果富人得到了政治优待,或者是通过破坏公共健康体制及公共教育体制,使得穷人在政治、健康或者教育方面利益受损,那么即便穷人最终赚到了钱,他们的实际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得更好。我们不能仅仅以物质水平一项来评价一个社会或者其公正性。但是,经济学家却经常错误地将帕累托法则用于分析收入问题,而忽视了人类幸福的其他方面。
当然,仅仅关注健康问题或者事关人类幸福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让亟须医疗救助的人获得救助,这些是好事。但是,在我们将健康放在优先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成本。我们也不能将寿命长短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寿命长的国家的人生活一般会更好,但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那么寿命长未必是福。
幸福与否不能仅仅看平均情况,必须要考虑不平等问题。同样,判断幸福水平的高低需要从整体出发,而不能只看到某个方面或者某些方面。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会就与幸福有关的自由程度、教育水平、社会自治水平、人的尊严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方面展开全面论述。不过,即便在本书中我仅仅是从健康和收入两方面去考察幸福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让我们摆脱单一论证的不足。
如果我们的祖先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肯定会喜欢我们如今拥有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们也毫无理由认为,过去的父母们会对子女夭折的现象熟视无睹。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对于此事,实际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可以去读读珍妮特·布朗的书。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死去时的痛苦。逃离苦难是人之天性,但是这种欲求却经常无法实现。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有时,灵感常常源于那些孤独的、幻想着弄出点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发明家们,但是更多的时候,创新不过是其他东西的副产品。比如,识字能力的普及是因为新教徒必须读《圣经》。同样更为常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会导致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满足需求。帝国时代的繁盛使得英国人的工资水平提高,而高工资加上英国丰富的煤矿资源,为发明家和工厂主提供了发明创造的动力,而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引擎。英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为即将出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19世纪的霍乱刺激了细菌致病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而今天,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艾滋病研究,解开了病毒的秘密并研制出了新的药物。尽管这些药物还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们已经大大延长了被感染者的寿命。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依靠灵感是解决不了的,而强烈的需求和动机也未能激发出神奇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解决方案。比如疟疾已经使人类遭遇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案。需求或许是发明之母,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有需求就必然有发明。
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20世纪70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中被发现。因为这种廉价而又易制的方法,数百万遭受痢疾折磨的儿童得以避免脱水以及可能引发的死亡。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势。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种新的制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则大难临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中国的皇帝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于1430年禁止了海上航行。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无独有偶,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铁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担忧铁路会输入革命,威胁王权。
不平等会促进发展,亦可能阻碍发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而各怀己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争论称,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关于何为机会平等,依旧众说纷纭。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在本书中,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
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对世界范围内健康与财富问题的描述,它的重点当然是今日的世界,然而也会转向历史,去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境况的。第一章是导言性质的整体描述。它将提供一张反映世界概貌的简略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地方的人们正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则没有如此幸福。它也将以详细的数字证明,这个世界在减少贫困和降低死亡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这些数字也将说明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而是在生活条件、生存机会以及福利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部分的三章讨论健康问题。这三章将考察过去的历史如何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状况。人类曾经以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度过了几百万年,这些岁月会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世界人类的健康现状。而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人口死亡率下降,其所开创的生活范式,也对当代的健康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7 000至1万年前农业的出现,让人类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但是也带来新的疾病,等级制国家体系取代人人均等分配的狩猎采集组织,新的不平等随之而来。在18世纪的英格兰,全球化带来的新药物、新疗法,让很多人得以保住生命,然而能保住生命的人,多数也是因为他们支付得起这些新治疗方法的昂贵费用。虽然这些新的医学手段最终普惠了每一个人,然而普通人的生存机会从此却不能与上层贵族相提并论。到19世纪末,细菌致病理论的发展以及被接受,为新的爆炸性的健康进步打下了基础,然而也制造了新的生存机会鸿沟。只不过这次,不平等是发生在富裕国家的人民与穷国的人民之间。
我会阐述那些落后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在“二战”后出现的死亡率下降是一次进步,也是一次追赶,它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那条始自18世纪的生存机会鸿沟。这一努力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抗生素的使用、瘟疫预防、疫苗接种以及干净的水,挽救了无数儿童的性命。人的预期寿命有时可以一年提高好几岁(从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仍然存在。可怕的倒退经常出现。而近几年艾滋病的蔓延,也使得非洲数个国家在过去30年中对抗死亡率取得的进步毁于一旦。即便没有这些灾难出现,还是有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横在眼前:很多国家仍然没有完善的体系提供常规的卫生保健,很多孩子仍在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了“错误”的国度。而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仍有一半的儿童还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富国与穷国间死亡率的差距并没有完全消弭,因为富裕国家的死亡率同样也在下降(这是好事)。不过,在富裕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因与穷国不同,它并非是依靠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因为成年人寿命的延长。在关于健康内容的最后部分,我会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富裕国家的死亡率是如何下降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原因何在;吸烟在健康问题上扮演了何种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及为什么我们对心脏病的预防治疗远远比对癌症的治疗要成功得多。在这里,我们将看到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幕又重新上演:健康不平等随着健康的进步而再次出现。
第二部分的两章主要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我将从美国开始论述。虽然美国的确非常特殊也经常走极端,但是,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等问题上,影响美国的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富裕国家。“二战”后,经济增长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繁荣,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一个年代比一个年代慢,直至2007年出现经济大衰退。战后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尤其是让非洲裔美国人和老年人受益,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并未出现明显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可以说是现代主要经济体的典型标本。但此后,美国的故事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经济增长放缓,而不平等状况却因为顶尖富人群体的收入飙升而变得更严峻了。与之前一样,不平等也有其好的一面,这一次,是它使得教育、创新以及创意活动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它也有黑暗的一面:富豪的主宰给民众福祉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威胁。
我还将以世界为整体来考察人类的生存状况。从1980年起,全世界的贫困区域大幅减少,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也肯定是速度最快的一次。这一盛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优异表现。得益于经济增长,中、印两国已经改变了超过10亿人的生活。人类贫困减少这一结果或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悲观预测大相径庭。当时,人们以为人口爆炸将使世界陷入灾难,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当年悲观的预测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10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人已经胜利逃亡,还有一些人被抛在了后面。
第三部分只有一章。作为结语,我将在这一部分结束我的探讨,并转而阐述我们应该如何有所为,以及如何有所不为。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我坚信,作为有幸出生在“正确”国家的人们,我们对于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与疾病,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些已经胜利逃亡的人,或者至少是依靠前辈们的努力胜利逃亡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仍深陷困境的人。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道德义务的实现要依靠外国援助和国家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努力,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或者成千上万的非政府救助组织。依我之见,这些机构当然做过好事,比如与艾滋病以及天花等疾病的斗争就是极好的例证。然而我却越来越相信,多数外在的努力更多时候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外在的帮助是在阻碍这个国家的自身成长(我也相信的确会如此),我们就不能坚持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样的理由去继续干预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停下来。
后记是对本书主题的回归。它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影《大逃亡》的结局并不圆满,那么在真实世界里的大逃亡,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吗?
在本书中,我会尽可能以数据和图表来支持我的观点。若没有完整的定义以及证据支撑,则所谓的进步就不能得到清晰讨论。事实上,政府若无收集数据的意识,那就算不得开明。国家对人口的统计已有数千年历史,《圣经》中,玛利亚必须随约瑟回到其出生地进行登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在美国,政府规定每10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倘若没有这种人口统计,那么平等的民主就不可能存在。不仅如此,在更早的1639年,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就要求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做精确的统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关键数据,公共卫生政策也必然是盲目的,不能有的放矢。
对于穷国而言,目前它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法掌握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更不用说掌握人口死亡的原因了。来自各种国际机构的数据倒是不少,然而人们却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随意编造的数据对于政策制定或是外援评估,都是不够可靠的。人们意识到急需要做点什么,但却对具体做什么没有足够的理解。没有数据的佐证和支撑,任何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以宣称是有成效的。我在后面的正文中,将努力阐述我那些基于数字的证据,并说明其来源及可靠性。当然,我也会有数据支撑不足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尽力使我的观点合理化。
在处理数据时,我们需要尽力弄清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何在,否则,我们就容易犯无中生有的错误,还可能遗漏一些紧急而明确的需求。我们需要警惕,不能被虚假的幻觉所欺骗,而忽略那些真正可怕的东西;我们也需要谨慎,不要提出一些会从根本上产生误导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人类的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水平主要是通过收入,即人们消费与储蓄的那部分货币来衡量的。货币的价值会根据人们的购买成本进行调整,在调整之后,货币就变成一个可以用于衡量人们购买能力的合理指标。当然,很多观点认为,我们对收入的重视程度过高了。的确,美好的人生不只是拥有金钱。但是宣称钱不能让人过得更好,这种观点就未免过于偏激了,至少钱让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持“金钱与幸福无关”这种观点的人所依靠的证据是,曾经有关于快乐的调查宣称,除了对于那些深陷贫困的人,钱很难或根本就不能让人感到快乐。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快乐是一种衡量幸福的指标,那么我的大多数观点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讨论钱和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成了我展开论述的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引入了图解的方式,并把这种方式贯穿本书始终。
很多参与相关调查的人们会被问到,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如何,这样的调查经常与以“快乐”为衡量标准的调查混为一谈。这导致的结果是,调查里会出现不快乐的人却过着很好的生活,或者快乐的人却过着艰辛的生活这类结果。这样的调查犯了将生活满意度与快乐两个指标混淆的大错误。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各方面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总体评价,而快乐则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让人们评价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评价体系共分11级,最低为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差的生活,最高为1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好的生活。每位受访者必须回答觉得自己此时生活在哪一级别。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来分析不同国家间民众的生活水平感受差异,尤其是可以以此来考察,在这样的评估模式中,是否高收入国家的人们会感觉自己过得更好。
图0–1显示的是,2007~2009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调查所示的生活总体评价平均值与人均国民收入(更确切地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人均国民收入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之后的美元来衡量(在第六章中,我将详述这些数字的来源以及为何需要对这些数字的价值有所保留)。在图中,圆点大小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多少成正比。其中,左边两个最大的圆点分别代表中国内地和印度,而右上方较大的圆点则代表美国。在图中,我还标注了其他一些值得特别留意的国家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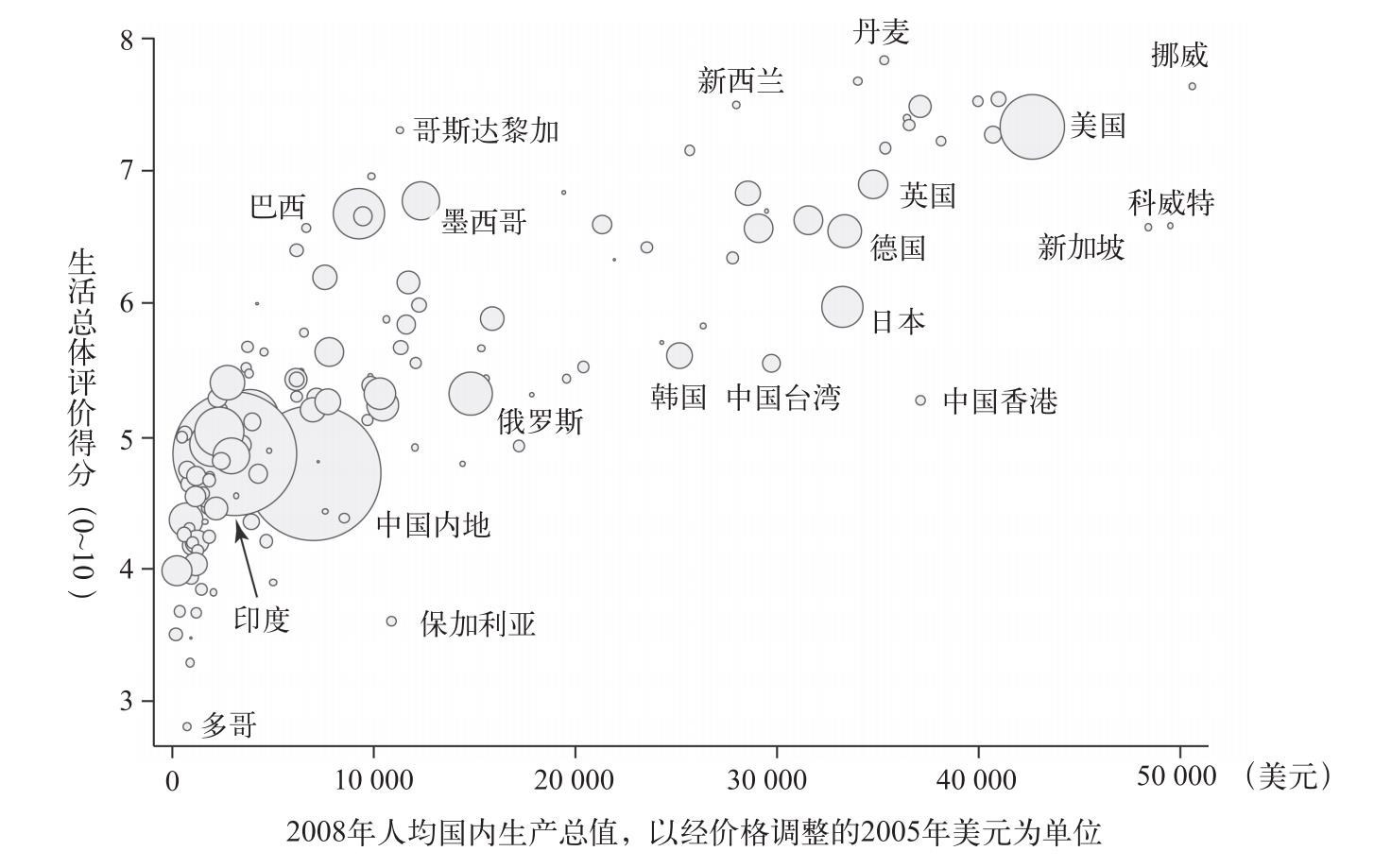
图0–1 生活总体评价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图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左下方生活在最穷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常对他们的生活总体水平非常不满意。他们不但收入低,也自认为总体生活状况很差。而在世界另外一端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人们不但拥有高收入,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总体状况很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生活总体评价最差的是多哥。多哥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里的人民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评价最好的国家是丹麦,这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国度。在这些指标比较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均值都高于美国,不过美国也处于平均值最高的区域之中。这种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评估存在很多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的总体评价都不高,其中尤以保加利亚最为典型。但是同样收入较低的拉丁美洲,却对生活总体评价很高。这说明,收入并非是人们评价生活状况时唯一考量的标准。
观察图中左下方贫穷国家和地区分布密集的区域,我们会发现,对生活总体的评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快速上升。但是,当我们跨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左往右看,生活总体评价分数的增长就变得稍微缓慢下来。巴西和墨西哥的分数大概是7,这与右边的富裕国家和地区仅仅相差1分左右。可见,收入对生活的影响,在穷国要比在富裕国家大。的确,单看此图,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钱对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之前提到的很多人便是持这样的观点。然而,这样的结论却是靠不住的。
钱的多少对于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同样影响巨大。要把这一点解释清楚,我们只需要将图0–1稍做调整。当我们在讨论钱的问题时,既可以以绝对值为单位,也可以以比例说话。偶尔,我普林斯顿的同事们相互之间会聊一下薪水的问题,他们会说,谁谁的薪水涨了3%,谁谁的涨了1%。实际上,系主任表达自己对员工满意与否,一般都是通过加薪的幅度来体现的,而不是加薪的具体数额。对于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来说,加薪1%的绝对数,比一个年薪5万的人加薪2%要高。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他会认为相较前者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更好(事实也是如此)。在此类计算中,百分比变成了一个基本单位;人们会忽略底数,而认为10%的薪水增长都是一样的。
对于图0–1中的数据,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但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过大,同以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相比,以4倍的比率来处理这些人均收入数据更为合适。这里,我们选择以250美元作为基数。在图中我们会发现,只有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处于250美元以下。乌干达、坦桑尼亚以及肯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在1 000美元附近。这正好是基数250美元的4倍。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又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4倍,也就是基数的16倍。然后墨西哥和巴西又是中印的4倍,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又是它们的4倍。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相比,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了256倍(在第六章中我还会解释,其实这些数字仅仅是个概数)。一言以蔽之,在图0–2中,我们放弃了以绝对数字作为标准来评估人们的生活水平,转而以4的倍数为单位,进而比较处在基数的4倍、16倍、64倍以及256倍位置国家的生活水平。
图0–2中的数据与图0–1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人均年收入的数据现在以1倍、4倍、16倍、64倍和256倍来进行划分。我将这5个倍数分别以250~64 000的5个具体的收入数字加以标注,于是可以看到图表的横坐标轴上这5个数字从左至右成4倍倍数排列。从左到右每两个数字之间的距离是相同的,代表相同的倍数差别,而不是图0–1那种绝对数字的差距。这叫作对数标尺,我们之后会在多处用到。
虽然只是横轴发生了变化,但这却让图0–1看起来和图0–2有天壤之别。原先富裕国家之间的生活总体评价差异较小的趋势,在这里荡然无存。现在,所有的国家大体是沿着一条向上的斜线分布。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收入上同样比例的差异,导致了在生活总体评价上同比例的绝对变化。如果从一个国家移动到下一个人均收入4倍于它的国家,我们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比上一个国家也高出1分。而且,这种现象既出现在富裕国家中,也出现在贫困国家中。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指出,这里也存在很多例外,很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评价得分与其人均收入并未全然如预料的那样对应。不是所有富国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都高于穷国。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从整体上看,确实是每有4倍的收入间隔,生活总体评估的得分就会有1分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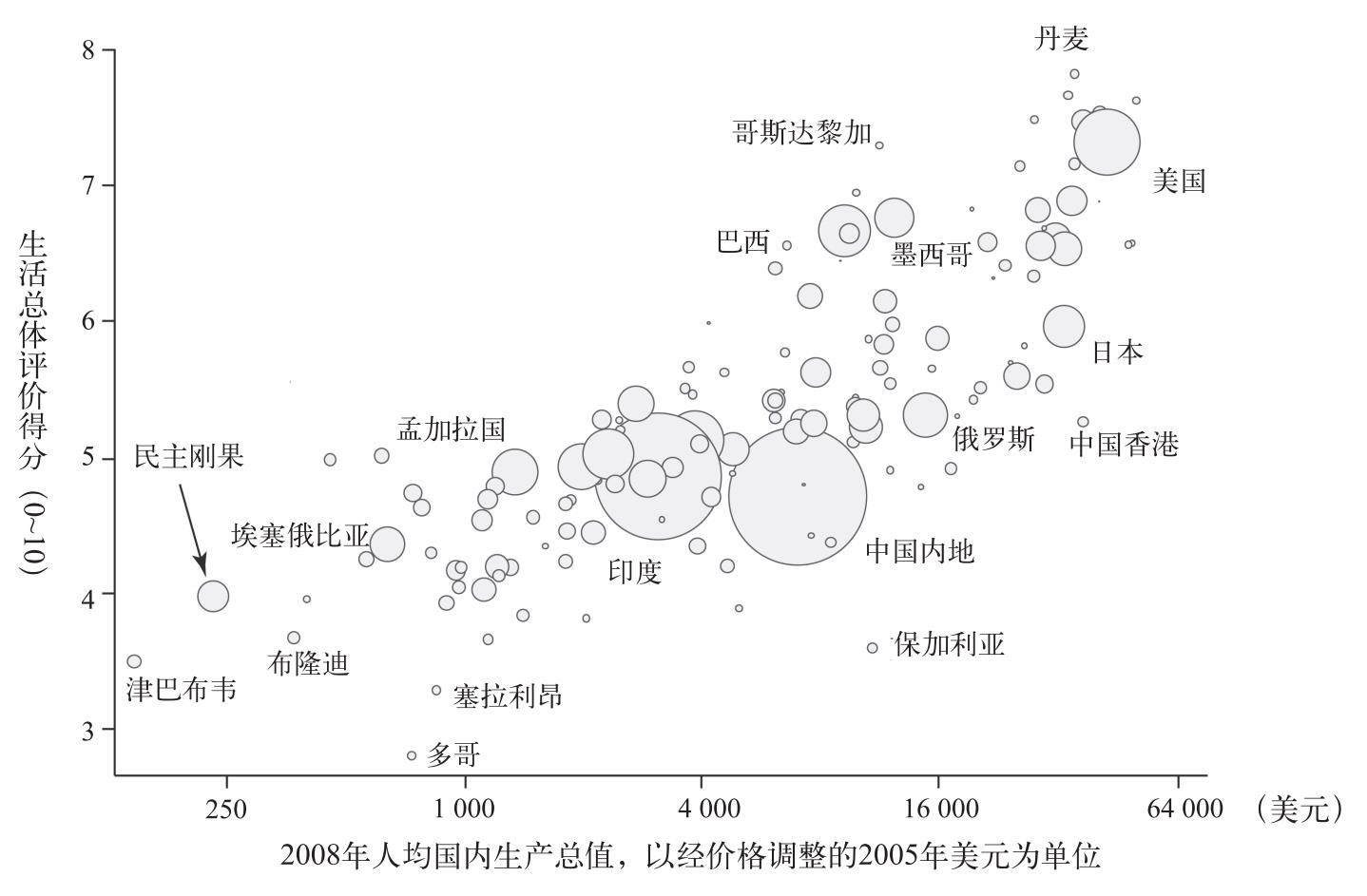
图0–2 对数标尺处理下的生活总体评价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到底是图0–1对,还是图0–2对?两者都对。这就如同一个年薪50 000美元的人薪水涨了2%,但绝对数只有1 000,而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薪水虽只涨了1%,但绝对数却是2 000。同理,在图中,虽然从刚果到印度,和印度到美国,看起来人均收入都是间隔4倍,但是后者的增长绝对数却要大很多。图0–1表明,同样的绝对数量收入增长,对于富国人民生活总体评价的影响要比对穷国的影响小很多。而图0–2则表明,同样倍数的收入增长,无论对于穷国还是富国,都会对生活总体评价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
对生活总体的评价显示出除了收入之外人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方面,也导致了一种金钱不足论的观点。能认识到影响人类福祉的,还有钱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健康、教育或者参与社会的能力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因此说金钱不值得讨论,或者认为相比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讲,钱不能增加富国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不准确了。而如果就此只认生活总体评价这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的评价标准,就更不对了。生活总体评价这种衡量体系还远非完美。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人们经常不能确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怎样的回答,而国与国的比较结果也会因为各国受访者回答风格的差异而受到影响。比如,在很多地方,“没什么可抱怨的”,或者“还不赖”这样的回答,大概是人们能做出的最多的反应。然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人们会更乐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掩饰自己生活上的成功。因此,图0–2也十分重要,它说明,关注金钱多寡对生活的影响,并非是一种误导。更富裕的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总体评价,这一点,即便在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也不例外。
在第一章,我会回过头来讨论如何衡量幸福与生活满意度这一问题,但我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从更宽广的角度考察当今世界人类的福祉问题。我将聚焦于那些已经成功摆脱死亡和贫困的人,但也绝不停留在此,因为我还同样关注那些仍身处困境等待一场生存大逃亡的人。
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几千年来,人们即便有幸逃过了童年早逝的厄运,也要面对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人类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寿命延长了不止1倍,过上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父亲的寿命,是我祖父一辈的2倍。他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得到的实际收入,与以挖煤为业的祖父相比,也增长了不知多少倍。而我所受到的教育和以教授为业所得到的收入又大大超过了我父亲。现在,全世界儿童和成年人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但是人类的大逃亡却并未完结。仍有10亿人遭受物质和教育匮乏之苦,他们的寿命与其先辈们(或者我们的先辈)相比,也没有增加。人类的大逃亡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比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更加富足,身体更健康,长得更高大,受的教育更好。与此同时,大逃亡也制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世界: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人类大逃亡的故事。大逃亡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需要为今日的世界不平等负责。本书同样会阐明,为了帮助那些仍然陷在困顿中的人们,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又不应当做什么。
我使用“福祉”这个词来指代所有对人类有益,以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它包括物质的丰富,比如收入和财富;也包括身心的愉悦,即健康和快乐;还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这本书的主要章节将聚焦于这些福祉组成因素中的两个:健康和财富。在这一章的总体论述中,我也会谈到一些关于幸福的问题。
在本章,我会对今日的人类福祉做一个概论,同时也会回顾在过去的30~50年中,人类的福祉是如何变化的。在这里,我会用最少的笔墨来呈现一些基本的事实。而在之后的章节,我会比较细致地探究每个具体的话题,阐述其中的缘由,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方式。
显而易见,健康是讨论福祉问题的起点。人得先活着,才能去想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身体不健康,或者任何的生存障碍,都会严重限制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从人的生存谈起。
如今,一个美国小女孩的预期寿命是80岁。实际上,官方的这一预测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未来人口死亡率会继续下降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降低,而这一步伐不可能突然停止。当然,要对人的寿命增长做出规划很难,但是,不是虚言,未来,一个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女孩活到百岁的概率有50%。相对于她曾祖母的时代,这样的寿命变化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曾祖母,如果生于1910年,则其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4岁。那一年,在美国出生的女孩有20%没活过5岁就夭折了;与此同时,每5 000个人中,只有两个能活到百岁。如果她的祖母生于1940年,则当时的预期寿命是66岁。在那时,每1 000个儿童中,有38个1岁不到就夭折了。
不过,与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相比,美国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距显得微不足道。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健康状况比美国1910年的情况要差。在塞拉利昂(或者安哥拉、斯威士兰、民主刚果、阿富汗),1/4的孩子活不过5岁,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在那里,每个女人一般要生5~7个孩子,而其中多数母亲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至少一个孩子死去。每有1 000个孩子降生,就有1位妈妈死亡。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将要生10个孩子的女性,其死亡风险高达1%。即便情况如此恶劣,与几十年前相比,这也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世界上条件最差的地方,即便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死亡率也已经出现下降了。不过在情况最糟糕的某些国家,比如斯威士兰,即便儿童能活过5岁,其到成年时期也得面对艾滋病的威胁。一般来说,成年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但是艾滋病大大提高了其死亡概率。当然,艾滋病蔓延这种恐怖情况在热带国家和最贫困国家都不算普遍,在那里,很多国家的新生儿存活率和美国的一样高,甚至更高。这里面就有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国家。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2005年,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上1/3的人口和近乎一半的最贫困人口),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
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会详细说明我所引用的数据的来源,但是,现在就有必要强调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越穷,其健康数据就越糟糕。不过,具体而言,在儿童的数据部分,我们有令人欣慰的信息:1~5岁儿童的存活率提高了。但是成人部分的数据,包括产妇的死亡率,以及15岁儿童的预期寿命,却令人忧虑。
健康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能活着或者活得寿命很长,它更重要的含义是活得好。好的内涵是多维度的,与人活着还是死了这样的事实相比,健康状况是否良好非常难以明确衡量。但我们仍有很多实例,证明人的健康状况在随着时代进步而提高,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与穷国的人相比,富裕国家的人承受的病痛和身体伤残更少。在富国,人口伤残率一直在下降,而人的IQ(智商)则随时代推移而逐步提高。在世界多数地方,人们的身高比以前增加了。但是那些在童年时代营养不良或者遭受病痛的人,却没有长到基因允许达到的高度。一个人长得比理论所预测的高度矮,一般都说明其童年不幸。童年时没能健康成长会损害脑部发育,从而也会影响其成年之后的发展。一般而言,欧美人要比非洲人高,也比中国人和印度人高。如今,成年后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要高。全球健康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全球不平等,从人的身高差距上就可见一斑。
健康差距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和贫困与否的反映。无论与1910年还是与1945年相比,美国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而那些人口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其民众的收入和美国人比起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民主刚果的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0.75%。在民主刚果,超过一半的人口每日的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与此类似的国家还有塞拉利昂和斯威士兰。因为战乱等因素,一些世界上生存境况最糟糕的国家甚至还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阿富汗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有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美国的贫困线是每日人均生活费15美元,比那些贫困国家高很多。我们根本没法想象,一个美国人如何能靠1美元过一天(不过有个数据说,要是扣除了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1.25美元也能让一个美国人过一天)。但是,那些穷国的人每天赖以生存的费用便是1美元左右。
预期寿命和贫困的关系的确存在,但并不明确。印度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但是在印度,有1/4的人口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在中国的农村,1/7的人口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但是论人均收入,中国仅是美国的20%。也就是说,1个美国人的收入大体相当于5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还有一些国家更贫穷,但是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很高。比如孟加拉和尼泊尔,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都是65岁左右。根据2005年的数据,越南的人均收入仅仅比这些国家稍好一点,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高达74岁。
部分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则与其收入水平毫不相称,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最富有国家当中,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排名末位。另一个类型的例子是赤道几内亚。2005年,这个国家依靠卖石油人均收入大涨,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低于50岁。赤道几内亚曾经是西班牙在西非的一块殖民地,目前处于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治下。若要评选谁是非洲最恶劣的独裁者,姆巴索戈当仁不让。他的家族攫取了这个国家依靠石油出口获得的大部分收入。
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人民免于贫困,而又有民主法治,这些是一个理想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主要特质。具备了这些特质,人民就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有条件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们没有做过调查,所以其实并不能确切地了解,人们到底最在意什么;也不知道在健康与金钱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权衡;甚至不知道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对他们到底是否重要。人通常有一种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可以在那些死亡率和贫困度都很高的地方拥有快乐的心态,甚至过上幸福的生活。穷人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也会觉得自己过得非常幸福,而富人看起来拥有一切,却可能对生活极度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以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概率来衡量他们的福祉,而不是以他们的自我感觉为准。一个穷人生活得开心,适应力强,这不能改变他贫困的事实。同样,一个亿万富豪觉得自己很不幸,或者贪得无厌不知满足,也不能改变他富有的事实。这种阿马蒂亚·森口中所谓对“能力”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们摆脱贫困的一种检验。这种检验的标准是以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而不取决于人们对个人境况的自我感受。当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这本身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知足开心总比愁眉苦脸要好。这样的感觉对过上好日子是有帮助的,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便在对福祉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会优先考虑这种因素。我们的这种立场,和一些功利主义者的想法是有差别的,比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所认为的,对幸福的自我评估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好的环境只有在能增进幸福的时候才是有益的,如果人们自己觉得快乐,那么坏的境况也未必就是坏的。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论调,但我们从引言的图0–1和图0–2中,已经能看到,在生活状况恶劣残酷、预期寿命低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完全说不上满意。而在那些生活富裕、预期寿命长的国家,民众基本上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我们需要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确定健康、财富和快乐的各自特点。这样做是为了找出总体特征,同时发现例外。很多例外是非常值得留意的。在发现总体特征这一方面,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于1975年最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最有价值的方法之一。图1–1是普雷斯顿曲线的重绘版,相关数据都更新至2010年。这张图显示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是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纵轴是男女总体的出生预期寿命。每个国家都显示为一个圆点,圆点的大小与国家人口多寡成正比。图中较大的圆点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而右上部分相对较小但已经算比较大的圆点是美国。从左下升至右上的这条曲线展现的是预期寿命和国民收入之间的一般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间,曲线急速上行;但到了生活富裕、人均寿命长的国家,这条曲线就变得平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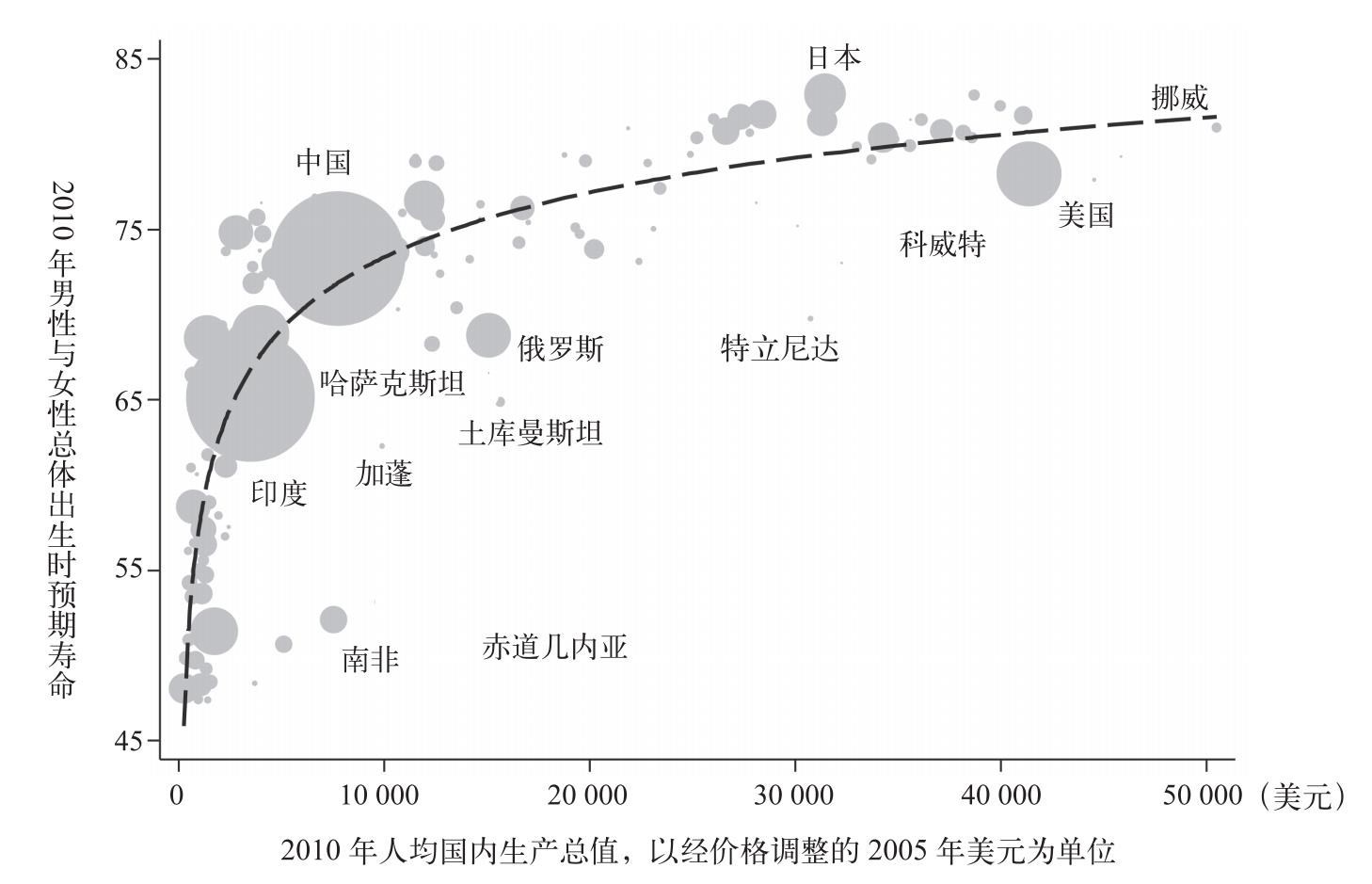
图1–1 预期寿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某一个国家内部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它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进行对比。这里使用的单位是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元。这样至少原则上能够保证所有国家1元钱的价值是一样的,从而我们就可以在相同情形下进行比较,即1国际元在巴西或者坦桑尼亚能买到的东西和1元钱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众多个人和家庭未能直接获得的收入,比如政府税收票据、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外国人的收入。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一部分(尽管是很大的一部分)可用于家庭购买支出,剩下的部分则以直接(比如政府的教育支出)或者间接(长期投资)的方式让普通家庭受惠。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意义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包含本国居民在国外创造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则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收入,但这一收入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区别,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比如卢森堡,在这个国家工作赚钱的很多是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这就使得卢森堡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世界上最大的赌城中国澳门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地区,和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类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一样,都被我们排除在曲线图之外。2010年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是绘制在曲线中,会在我们右侧的边界之外。相对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能更好地衡量国民收入,但是我们拥有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更为持续完整,因此,我在这里以及书中的很多处都选用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处的位置是整条曲线走势的“转折点”,这一点非常明显:从中国之后,原先走势陡峭的曲线开始变平缓了。实际上,这一转折点标志着流行病学转变的出现。对于这一点左侧的国家而言,传染病是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死亡人口中,儿童数量众多: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一半的死亡人口是5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曲线移动至富裕国家,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就变得非常罕见了,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开始占绝大多数。除此之外,传染病也不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慢性病,尤其是心脏病(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包括中风在内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在贫穷国家,慢性疾病也正在迅速成为更为普遍的死亡因素。不过,在富裕国家,除了少数老年人死于肺炎之外,如今只有极少人会死于传染病。这种流行病学转变被形象地归纳为疾病从婴儿的肠腔和胸腔转移到了老人的动脉里。
倘若要思考全世界的福祉分配问题,认识到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具备正相关关系十分重要。身体健康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图1–1证明了它们一般同向而行(尽管不是必然)。经受物质生活之苦的人们,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人,一般也正在承受健康之困:相对而言,他们的个人寿命更短,在有生之年,多数也要经历丧子之痛。而在曲线另一端的富裕国度中,人们则极少会经历子女死亡这样的悲剧,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而且生存寿命也要比最穷国家的人们长近乎1倍。当我们把健康和收入结合起来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福祉分化其实也是多重的。而人类真实的福祉差距,实际上也比我们只观察健康或者只观察收入所见的要严重得多。要认识这种真实的差距,一种粗略但通常行之有效(虽然毫无道德吸引力)的策略是把预期寿命和收入相乘,然后得出一个叫作终生收入的衡量指标。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衡量方式(由于一年的生命价值是以人的收入估价,一个富人一年的生命价值大大高于一个穷人一年的生命价值),但是它的确更形象有力地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例如,在民主刚果,一个人的收入大概只是一个美国人收入的0.75%,而其预期寿命则不到美国人的2/3,这样算下来,一个美国人的平均预期终生收入是一个刚果人的200多倍。
当然,这张图不能证明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不能确认疾病的发生都是因贫困而起。同时,这张图也不否认钱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收入的重要性,我会在后面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在很多方面,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个人要改善健康状况,就需要有更好的营养,也就需要花钱;政府要提供洁净的水源,改善环境卫生,也需要有钱。不过,在富裕国家,虽然科研耗费了很多金钱,但在癌症或者心脏病上的治疗效果却都不明显——这多少能解释过了流行病学转变这个点之后,曲线变得平滑的原因。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是有上限的(很多人竟然对此表示质疑),因此当人的寿命高到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水平时,要想再往上走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些观点经常宣称,在富裕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借鉴一下引言中提到的重新绘图的方式,把图1–1中的数据再做对数标尺处理,可以发现,虽然图1–2中的所有数据都和图1–1中的一样,但是却给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番图景:大体上,图1–2中的这条线左右两边的斜度是一致的,仅仅在右边最上的地方稍稍有些变平滑(大致是被美国的数据拖累)。这种情况说明,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还是和收入增长呈正相关的。这一点,和我们在引言中讨论生活满意度时所得出的结论类似。当然,由于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更高,因此同一比例的收入增长,其背后的绝对数额是不一样的。富国绝对收入的增长数额要比穷国的多很多。这就是图1–1所显示的,同样数额的收入增加,在富国中相应增加的预期寿命就比穷国少得多。但即使是在富国之间,更高的收入还是对应着更高的预期寿命。当然,图1–2的确显示出,各国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排序远远说不上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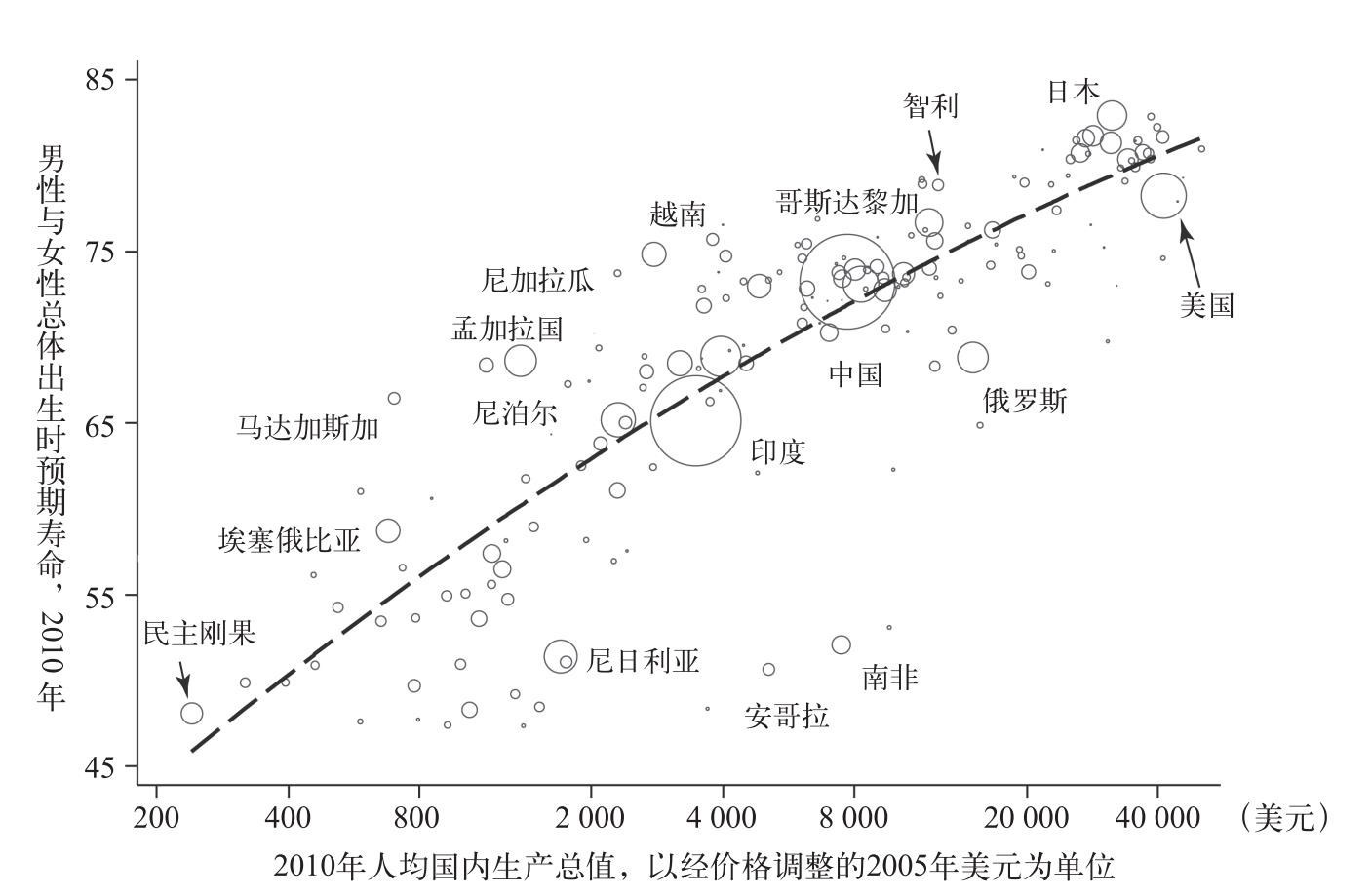
图1–2 预期寿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对数标尺)
那些远离曲线的国家,其背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比曲线附近这些国家少。有些国家是因为战争影响,人均预期寿命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以及其他没有标注的国家,则正在遭受艾滋病的困扰。其中的一些国家,“二战”以后在人均预期寿命上所获得的进步,已经被艾滋病的传播全部或几乎全部抹平。因此,在图上,它们的位置也就处在下方,远离曲线。我前面已经提过赤道几内亚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它的情况是所有国家中最为恶劣的。贫富差距也让南非处在图表中极低的位置。在艾滋病到来之前,南非就长期位于曲线之下了。南非地域广袤,整体贫穷,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却非常富裕。这种情况即便是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也长期存在。
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也表现不佳。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急速下降,这有转型所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原因。此外,过度饮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俄罗斯男性的影响尤为显著。俄罗斯的情况存在争议,因为在政治制度转型之前,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但不论真相如何,如今,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的情况,这与其国民收入极不相称。此外,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我们更难以衡量这些国家人民的收入状况,一些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看是有益的,但是在短期内的确造成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下滑。当然,与战后艾滋病的蔓延以及中国的大饥荒相比,俄罗斯的这些问题还不算严重,但是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福利水平也下降了。
美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表现也与其收入水平不相称。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却成为收入和健康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明证,更说明医疗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没有关联。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近,但是它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4,而其在医疗上的人均花费,也只有美国的12%。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我会进一步分析美国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支出问题。
其他国家的人均寿命表现则要大大好于其收入水平。关于这一点,图1–2比图1–1表现得更为清晰。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中国、哥斯达黎加、智利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其人均预期寿命在图中所处的位置,比我们根据其收入水平所预想的都要高。在以上这几个国家中,穷国家在控制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和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方面都做得相当好;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中老年人的死亡率通常都较低。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例外出现,但最主要的一点是:穷国可以做得比我们根据实际条件所预想的更好,而富国则可能做得非常糟糕。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在任何收入水平上,战争、流行疾病,以及极端的不平等都会让健康问题恶化。当然,与富国相比,前两种情形还是在穷国更常见一些。
图1–1和图1–2为我们展示了2010年世界的人口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图景。不过,预期寿命和收入的关系曲线从来没有停止变动。图1–3展示了两条曲线,其中一条就是2010年的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曲线,而另外一条是1960年的曲线。在图中,1960年的国家都以淡阴影表示,以便于和2010年的加以区别。每个圆点的大小和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成正比,但是仅限于在同一年份内的相互比较。因此,要注意,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年份圆点大小的变化不代表其人口规模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几乎所有深阴影的圆点都在浅阴影的上方和右侧。这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变得更加富有和长寿了。一切都在改善,福祉指标中的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在随着时光向前而提高:这也许是“二战”之后人类在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经济学家兼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对1700年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正是从1700年左右,人类开始逐步摆脱饥饿和早逝;而到了“二战”之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虽然到现在不少国家仍深受饥饿与死亡的威胁,而更多的国家还在为此目标努力,但那些业已取得的成就仍然值得予以关注和庆贺,毕竟数以亿计的人口已经摆脱了疾病和物质匮乏的困扰。阿马蒂亚·森将人类所取得的进步称为自由的获得,如此,则如图1–3所示,2010年的世界比1960年的更加自由了。如果在这张图中继续加入1930年或者1900年的相关数据(这些年代的数据不够完整),我们也会看到,实际上从250年前直到现在,人类的自由程度一直在扩展,并且扩展的幅度一直在加大。在最近的半个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获取自由的行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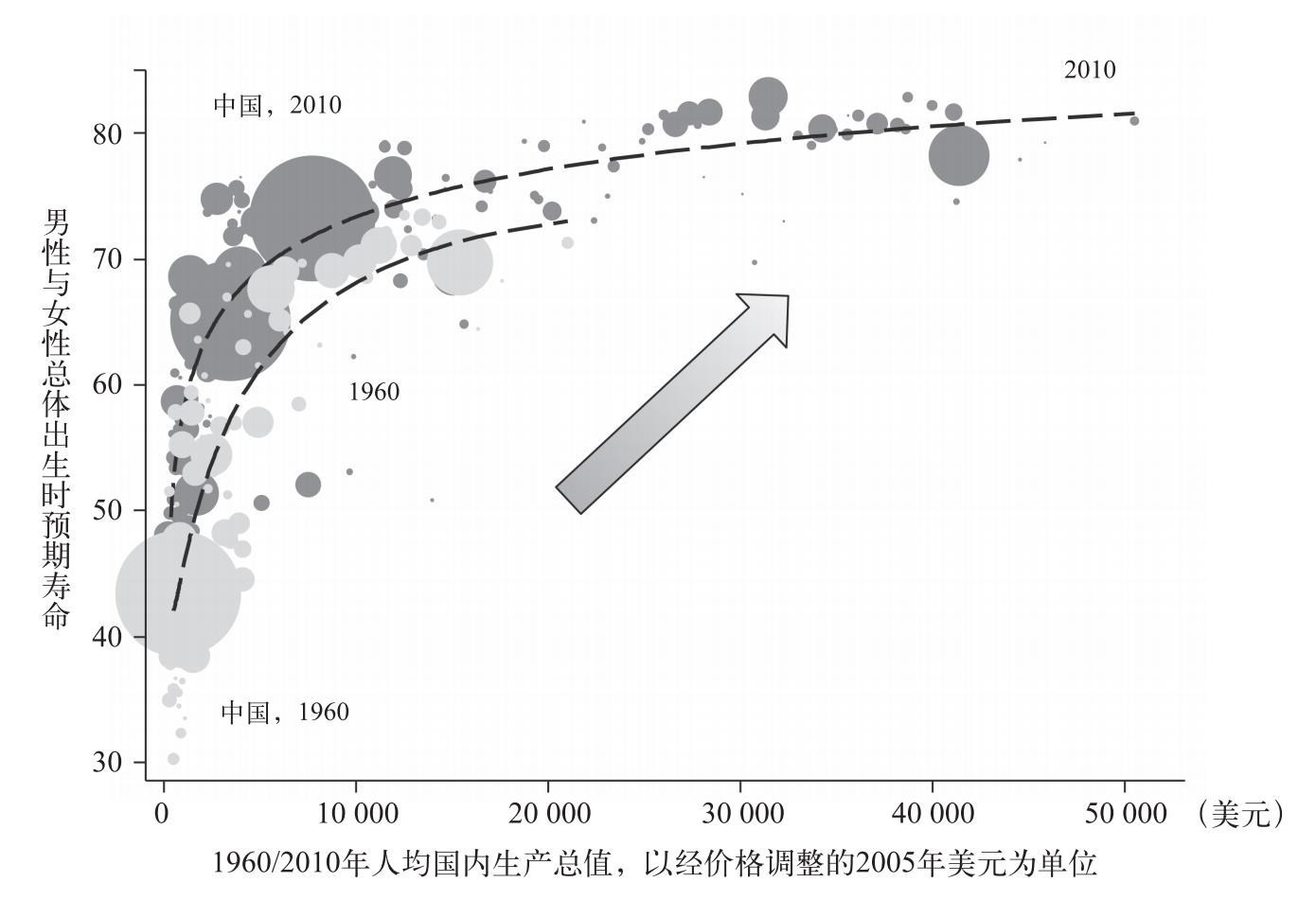
图1–3 更富裕,更长寿
总体上看,人类在进步,但是中间也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发生在1958~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在这一时期,错误的工业化和粮食收购政策导致数千万人口被饿死,同时,新出生人口的数量也减少了数千万。在这几年中,气候条件并无太多异常,这场大饥荒纯粹是一场人祸。
艾滋病的蔓延则是另外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导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上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急速下降。南非在图中的位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在图1–1和图1–2中,南非远在曲线之下。但如果回到1960年,我们会发现,即便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的影响,南非所处的位置也很低——这说明,南非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不是因为疾病的拖累。实际上,南非的问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如果我们观察不同年代的曲线变化,就可以发现,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南非在图表上离曲线越来越近,而不同种族的健康水平差异也在缩小。至少在1990年之前,这种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在此之后,因为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南非再次远离曲线,落回到图1–1中的最初位置。
在过去几年中,抗艾滋病药物的使用使得非洲的死亡人数得到了控制。这场流行疾病提醒我们,人类任何的“大逃亡”都可能是暂时的,传染病的大流行并不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中世纪有黑死病,19世纪有霍乱流行,如今则是艾滋病。无论是学术刊物还是大众媒体,都过分关注当下的威胁,而忽略了某些“新兴”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像艾滋病这种由动物传染给人的病症。实际上,我们身边存在大量的“动物传染性”疾病,而且其中的一些是极为致命的。虽然大多数这类疾病不可能发展成大瘟疫,但无论如何,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比如艾滋病,虽然传染性低而且不会导致暴毙,但确实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这类病的流行,足以提醒我们在未来不能对类似的病症掉以轻心。
若是抛开各种灾难所造成的发展中断,我们可以从图1–3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各个国家都变得更加富有和健康之外,预期寿命和收入曲线本身也在随着时代前进而上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的曲线位于1960年的之上。不仅如此,实际上1960年的曲线也要高于1930年的,而1930年的也高于1900年的。普雷斯顿注意到了曲线的向上趋势,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为收入在增长之外,还必定有某种系统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人均收入是影响寿命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曲线就应该随着收入增加而向上,或者因收入下降而向下。但现实情况是,当曲线上移时,某些国家的收入却未必增加。因为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即便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普雷斯顿将这种曲线的上移,归因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进步,或者至少是因为现有科学和医学知识得到了更为实际的运用。他认为,曲线旁这些国家的变化应归因于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曲线本身的上移则得益于新知识的应用。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这是将贯彻本书始终的一个话题。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却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虽然全世界多数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必然带来贫困消减。有可能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的经济增长——不少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就是如此;还有可能,虽然国家经济增长了,然而只有国内的先富者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人常常用以上一种或两种情形作为论据,来证明他们所坚信的一个观点: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只让富人得利。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令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水平差异,而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也触目惊心。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平等是在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吗?是每个人都从增长中受益了,还是先富的人群持续领跑,将那些缺乏运气的人进一步甩在了身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就是看一看原先贫困的国家是否取得了比富裕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那么穷国的增长肯定要比富国快。如果说是科技与知识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那么在科技与知识可以得到便利传播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便应该越来越接近。
图1–4中这些看起来随机分布的小圆点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家。纵轴表示人均增长率,横轴表示人均初始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深色圆点表示每个国家在196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浅色点则表示这些国家在197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从图中可见,这些圆点毫无规律可循,也就是说,穷国的增长速度比富国更快这个说法无法从这张图中得到证实;而穷国追赶上了富国,以及贫富不平等在缩小这样的结论,就更无从得出。当然,反过来说,这张图也不能说明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比穷国更快。一言以蔽之,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多少。从图中可以看到,近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是正数,分布在零增长这条虚线的上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世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2010年,只有4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60年的水平,只有14个国家低于1970年的水平。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有几个表现最差的国家(比如陷入战争的部分国度)没有被纳入统计中,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相关数据,但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是近几年刚诞生的新国。在图1–4中,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是民主刚果和利比里亚,它们常年遭受战乱之苦。
对于同样的数据,还有一种不同的且更为乐观的看法。图1–5是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绘制的。这张图与图1–4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图中代表每个国家的圆点,因为与各国数据统计之初的人口规模成比例而变得有大有小。以这种方式进行观察,我们似乎可以很快得出一个负相关的结论,即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事实!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图中几个代表大国的圆点太大所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极快,这让超过20亿的人口平均收入脱离了世界收入分配水平的底部,并向中间水平靠近。如果视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其每个国民的真实收入,那么即便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图1–5也可以看出,全球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向着一个中心靠拢。但现实是,每个国家的个人收入不可能都相等,世界上不但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国之内,收入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会详细讨论。一旦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被纳入讨论,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变化这件事,无论有多么好的例子,都将变得更加难以说清。
当然,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但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更重视的是人而不是国家,那么的确可以说,乐观的图1–5比悲观的图1–4更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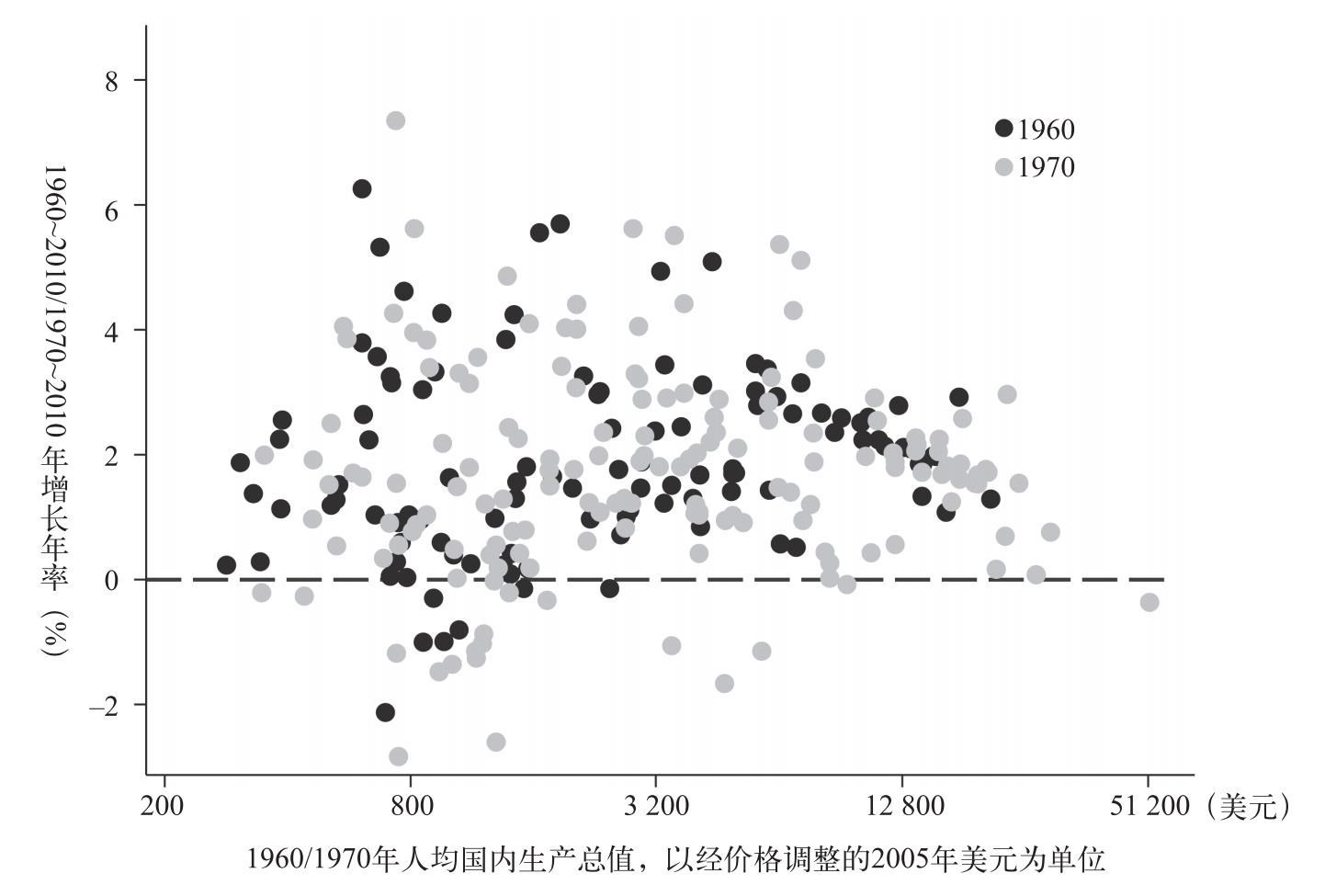
图1–4 各国的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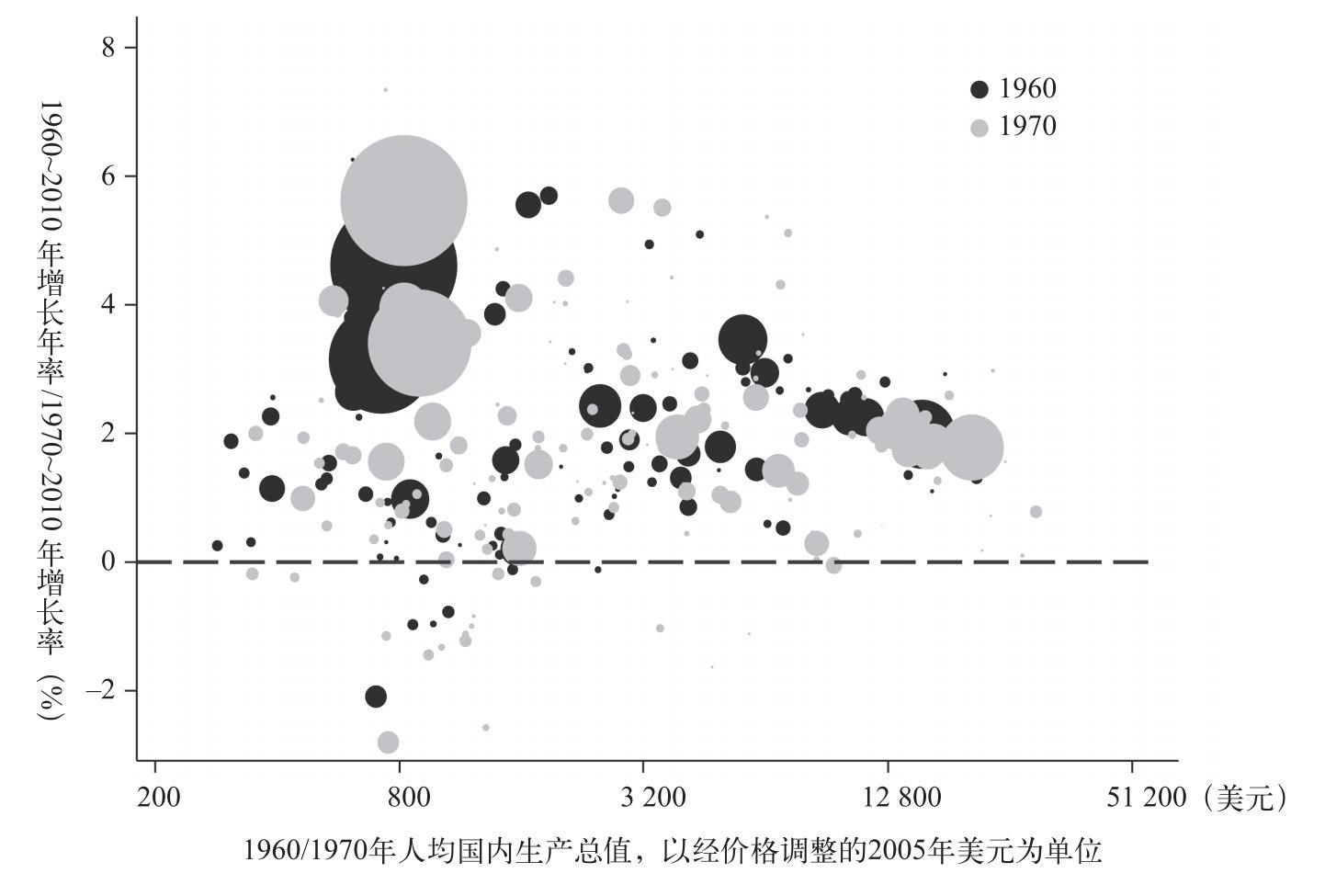
图1–5 考虑到国家人口权重的经济增长
全球贫困状况的改变,也与印度和中国密切相关。世界银行会定期统计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人口。图1–6就是根据2008年的最新统计数据绘制的。数据显示,尽管全世界穷国人口在1981~2008年间增加了20亿,但是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却减少了7.5亿。这意味着,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从40%降低到了14%。不过,尽管很多地区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世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在过去10年的下降却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是有所增长的(在第六章我们会提到,印度统计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这个说法似乎低估了印度在降低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根据世行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3年49%的峰值下降到了2008年的37%。非洲的经济水平虽然较低,但是近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总而言之,在全球范围内的消除贫困方面,我们取得了总体性的进步。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在所有的时间都有进步,但是持续近1/4世纪的经济增长的确大大减少了全球的贫困人口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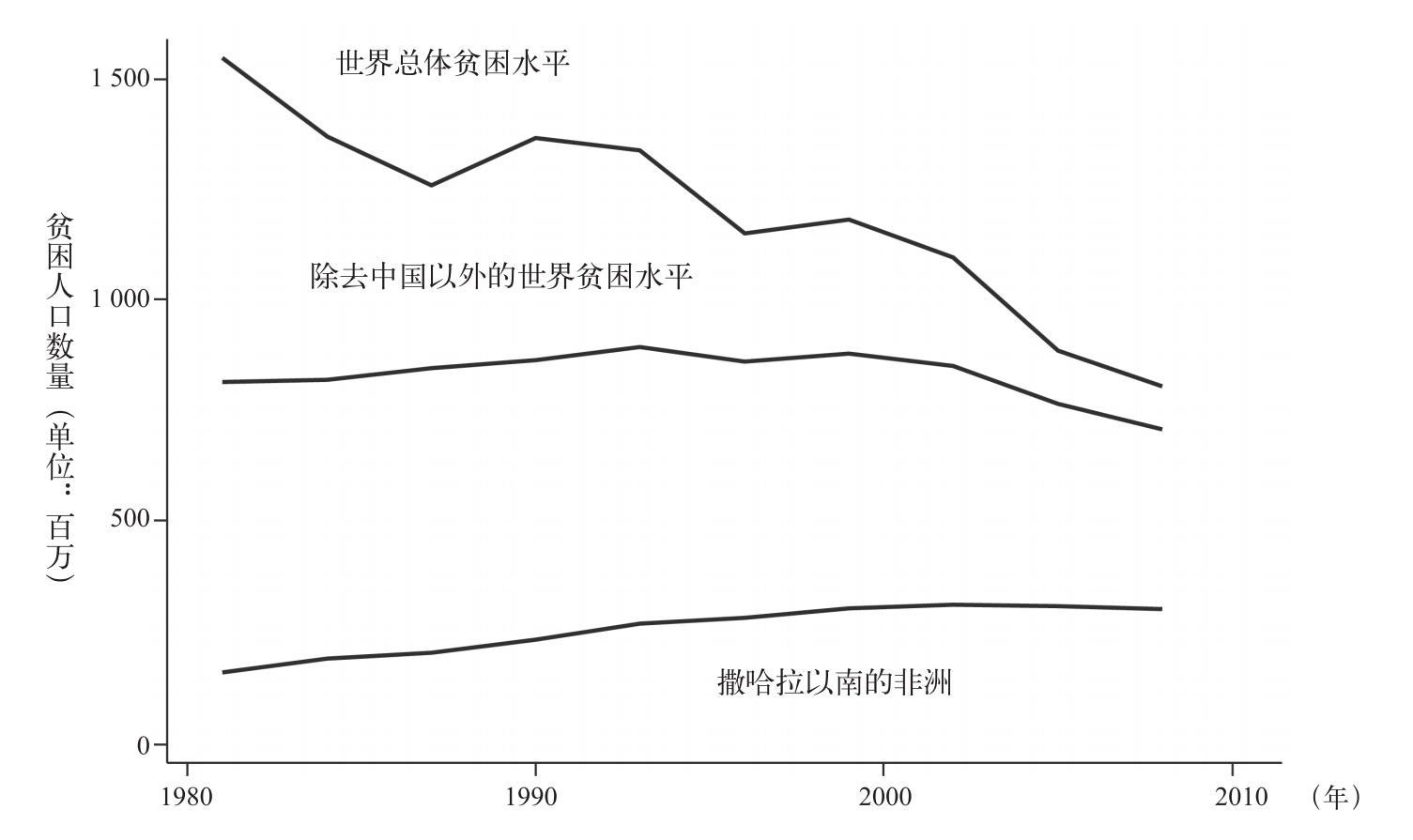
图1–6 世界贫困水平在下降
美好的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健康的身体和足够的金钱。要远离贫困,人类也需要拥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公民事务的能力。虽然我主要讨论的是健康和收入问题,但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当然,要做的事情仍然有很多。如今,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学校,文盲人数比以前大大减少。尽管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独裁统治,很多人参与公民事务的权利也仍然受到限制(有时这种限制甚至是极为严厉的),但人们总体上比半个世纪之前有了更多的政治自由。以环境所允许的程度看,多数国家人们的生活都已变得更加美好。这种生活也经常被专家或者学术评论者过分赞美,不过,人们并不一定以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要素作为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指标。人们本身对生活的意见被忽略了。有时候,人们也经常认为某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却从未将其考虑在内。因此,有必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幸福与否的感受。
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将人们对生活的自我感受作为评估其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引言中,图0–1和图0–2就是这样的范例。如今,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哲学家都开始看重这种对幸福的评估方式,很多统计官员也开始将其列为常规数据加以收集。这种评估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幸福感评估,其本身的确有不少特别之处,比如直接来自接受调查的人,更关注实际的结果,通常包括一些影响人的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知道也无法评估的。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自我陈述型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并不总能了解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并且,不同的人或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也经常不尽相同。即便是直译,对一个问题的翻译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对“幸福”这个词的使用比较随意,而法国人却不是如此,东亚人则很少表达说他们过得很幸福。在美国,追求幸福是《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我的出生地——信奉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乡村,有这样的追求会被认为性格过于懦弱。
适应性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生活在绝境中的人倾向于相信,眼前的生活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所以会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而那些生活奢靡的人,已经适应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哪怕是少了些许奢侈用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充实的生活往往也伴随着痛苦与失去,哲学家玛莎·娜斯鲍姆曾经写过“幸福勇士”的故事。勇士们奔赴战场,除了伤痛与可能的阵亡之外,别无所求,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样的生活美好而有价值。当然,对这些可能的情况持保留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而是要注意这些现象可能忽视了某些潜在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毫无疑虑地接受。
如果人们总是进行自我调节,满足现状,那么我们调查得到的反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差异。世界上多数富裕国家,其富庶通常已持续多年,而穷国则是困顿多年,若人们总能自我适应,那也应该早就适应了自己的处境。但是,本书引言已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
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丹麦以7.97的高分(得分以0~10的阶梯状排列)位居世界第一。在所有相关排名中,丹麦一直稳居第一。其他的北欧国家,芬兰7.67分,挪威7.63分,瑞典7.51分。美国以7.28分排在这些国家之后。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多哥仅得到2.81分,而经历了长期内战的塞拉利昂是3分,另一个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津巴布韦,得分为3.17。布隆迪3.56分,贝宁3.67分,这个悲剧性名单再往上列就是阿富汗,得分为3.72。这种生活总体评价方式的确遭到了质疑,但是,当用这种衡量方式来评估国家的贫穷程度以及辨识国家的贫富时,其结果和以收入水平、健康水平或者政治自由度高低为衡量标准的结果是极为一致的。富有而民主的欧美等国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等地的穷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就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与我们考察人们的收入或者寿命所得到的结果一致。
如果能够获得过去半个世纪的生活总体调查数据,就可以从历史入手,通过对比去发现1960年至今人们对生活自我感受的变化路径。之前我们考察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时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可惜盖洛普的世界调查开始于2006年,虽然之前也有一些来自某些国家的分散数据,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无法确认,调查样本的选择标准也无从得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认,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即便如此,富国居民对生活的整体评价要比穷国居民的高。这一事实容易使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回头再看对生活总体评价上的两极:丹麦和美国,以及另一极的塞拉利昂、多哥、津巴布韦,恰好一边是富国,一边是穷国。富国实现了250年的发展,穷国却一直毫无变化,而这正是对生活评价两极化的原因。我们之前提到,国与国之间的人均预期寿命存在巨大差异,而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如此,要是中德日美这些国家在2008年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比1960年的低,那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起来毫无争议的事情,却一直遭到质疑。
1974年,最早采用自我报告方式调查人类幸福感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指出,根据调查,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而觉得自己过得更幸福。后来,伊斯特林又通过在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调查,拓展了他的这一结论,即经济增长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善人类的命运。伊斯特林的经济增长无用论,在经济学界是相当罕见的。(不过,人类的健康和其他方面虽然未必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但是的确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质疑。)但是,许多人口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其他否认物质是幸福之基础的人士,都对伊斯特林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不过,那些处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们宣称,合理的参照数据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种关系,同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是类似的。
比起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经济增长对同一个国家内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难被观察到。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源于数世纪的经济增长差距,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即便是持续50年的经济增长,也未必能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在半个世纪之内以2%(图1–4中的平均增长速度)的速度持续增长,那么最终其人均国民收入会比最初时增加2.7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大概相当于今日印度和泰国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和收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在出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增长幅度较小、难以察觉甚至出现倒退,就并不稀奇。如图0–1所示,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印度的2倍,然而其国民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却低于印度。
正如在有的国家,人的健康水平并非一定与其收入成正比,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并不是经常和收入高低完全对应。我们已经知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幸福指数超级明星,也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它们的国民在生活总体评价上的得分与其收入水平是大致匹配的。但是,拉美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却常常超过其收入水平;而在亚洲,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与地区,人民生活满意度却常常表现得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相称。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地区差异因何而起:是因为它们在幸福的某些客观方面的确存在差异,还是因为国民的性情有别,还是因为不同国家国民回答问题的方式不同?我们发现,在俄罗斯、前苏联国家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些国家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活尤其不满意。在这些国家,年青一代拥有了先辈们无法企及的各种新机遇,他们有机会旅行、留学或者在全球的舞台上展现才华。而同时,他们的祖父辈们却眼见着自己所熟悉的、为他们的人生定义的那个世界崩塌了。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要承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不足的痛苦。
尽管在阶梯式问卷调查中,“幸福”一词从未被提及,生活总体评价还是经常被理解为是对“人是否幸福”的调查。事实上,生活总体评价是想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它询问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得到的调查结果说明人们对这些方面的心理感受不尽相同。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接受的时候,也依然会有不开心、忧虑,或者紧张的感觉。事实上,悲伤、痛苦与压抑几乎是人们要获得美好生活的必修课程。参加陆军新兵训练营、攻读经济学或者医学学位,或者是眼见父母逝去,这些是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的苦闷。青年人约会失败,似乎也是其情感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过程。过去高低起伏的情感经历,都为人生当下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当然,开心总比觉得难受要好,即便是紧张、担忧以及愤怒等不快的情感体验,也可能在未来给我们以幸福的回报。不过处在这些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
既然可以就生活总体评价进行调查,自然也可以就人的情感体验进行调查。盖洛普在调查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时,还试图了解人们在接受调查前一天的情绪和感受,担忧、紧张、悲伤、抑郁、快乐、愤怒、痛苦等,结果发现,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回答与其对生活总体评价的回答,简直有天壤之别。
图1–7是全球幸福分布图。图中,横轴指标是人均收入,纵轴指标是感到幸福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张图和生活总体评价图差别很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张图显示出人是否幸福和收入水平并无必然关联。虽然在几个最穷的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布隆迪、马达加斯加以及多哥等,它们的国民确实觉得不幸福,但是除了这些最穷的国家外,很难看出富国和穷国之间人们的幸福程度有规律性的差别。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但是却并没觉得很幸福。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与丹麦人或是意大利人相比,多数孟加拉人、肯尼亚人、尼泊尔人以及巴基斯坦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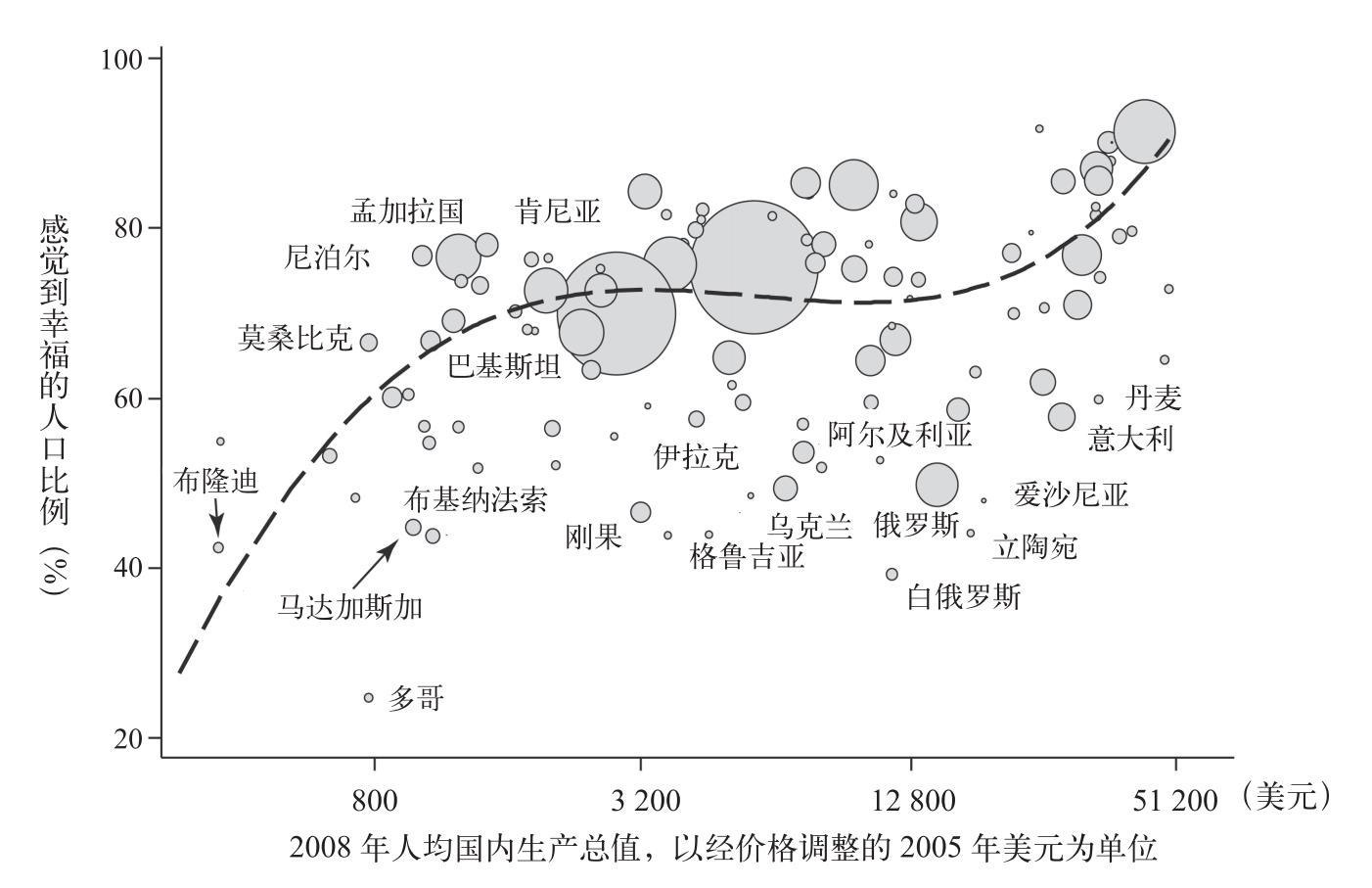
图1–7 全球幸福分布图
美国的数据也证实了人均收入和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贫困会让人处于悲惨的境地,然而当收入超过了一定的水平(约70 000美元一年),虽然使得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提高,却不会让人觉得更幸福。钱只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幸福,没有钱而心里感到幸福也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是否幸福却不能作为对人类福祉进行综合测定的有效标准,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即便人们深处贫困或者健康状况不佳,也有可能心情愉悦。对于人类福祉的综合测定而言,生活总体评价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刚才提到的丹麦和意大利就是两个能证明这一点的极好例子。
图1–7显示,美国人的幸福度仅次于爱尔兰和新西兰,居世界第三位。快乐对于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公民责任。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则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当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得比较开心,调查显示,全球近3/4的人口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其他的一些关于人类情感体验的调查,则展现了另外的景象。2008年,全世界19%的人认为自己在接受调查前的日子里过得很幸福,30%的人认为自己过得紧张,23%的人认为自己过得很痛苦。相对而言,穷国的人们过得更痛苦,但是快乐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相当复杂。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收入水平高低并不是正相关关系。比如,3/4的菲律宾人表示生活得很焦虑,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居民、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及美国人。有44%的美国人表示在接受调查前过得很沮丧。这说明,收入高并不能减少这类负面情绪。
对生活总体评价与幸福度(或其他方面)的调查,给我们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图景。那么,这两者哪一个正确?可惜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期望用单一的方法对人们的幸福程度做出评测,这是不切实际的,不是一种考察幸福的正确方法。快乐是一种好的情绪,忧虑和愤怒是不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生活在改善也是正面的,但这些感受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和人的收入以及身心状况等方面密切相关。在对幸福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种神奇万能的方法。即便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腕表一样的测量仪,把人的每一次快乐心情都记录下来,我们也无法用这些数据来评估我们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人类的幸福有多个维度,它们彼此关联但又绝不相同。在对全世界的幸福进行评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要利用好这一点。
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曾著书讨论英国人在追求个人成就上的观念变化。他指出,对财富的追求在18世纪变成了英国人寻求幸福的合法路径。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对财富的追求不但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个人活动,也同样使得整个社会受益。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也已经成为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一部分。当然,正如托马斯所提到的,对于个人是否能从财富中受益,斯密其实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斯密指出,尽管财富“让人类工业兴起并发展”,但是财富能带来幸福这种说法却带有欺骗性。他同样怀疑不平等的真实存在。他说,富人通过雇用其他人而“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却带来了“生活必需品”大致平等的分配。而至于富人,他们的财富“可以遮挡夏天的阵雨,但是挡不住冬天的风暴,而且,常常使他们同以前一样,甚至有时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
斯密写这些内容之时,正是“大分流”开始的时代。在当时,富人和穷人一样面临着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贵族的预期寿命也并没有比穷人更长。即使是今天,穷人在生活满意度上大大低于富人,但是在情感体验上却与富人依然没有什么差别。富人还是脱离不了紧张、害怕、悲伤这些情绪,也不可能每天都过得开心和享受。可是,在这250年间世界变了。没有合理的证据说明,“生活必需品”在今天的世界得到了平均分配——其实在斯密的时代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在如今,财富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保护,使人得以远离疾病与死亡的危险。尤其是在过去的60年中,人类整体上变得更加富裕了,对这个世界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而财富与认知所产生的保护力量,惠及了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广泛的人口。
自“二战”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人口的收入和健康水平都提高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或者儿童死亡率高于1950年。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点在中印两国最为明显。当然,这中间也有多次的逆流。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艾滋病的蔓延、苏联解体以及绵延不断的战争、杀戮和灾荒提醒我们,疾病、战争以及恶政的幽灵并不仅仅飘荡在过去的历史之中。拥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绝对是草率的,正如我们在《大逃亡》这部电影中所见到的,大逃亡未必能带来永久的自由,它通常只是暂时地让我们远离周遭的丑恶、黑暗以及混乱。
今 日人类的健康水平,几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人类的寿命更长,长得更高,身体更强壮,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也都在下降。健康水平的提高,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更有效率地工作,赚更多钱,也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新知,和家人与朋友一起度过更多更美好的时光。健康水平不像温度高低那样可以用数字简单描述。有的人或许视力很好,但体质虚弱;有的人可能活得很长,但却要忍受周期性抑郁或偏头痛的折磨。任何由健康因素所带来的限制性影响,取决于人的工作性质或者想要从事的工作类型。比如我的投球水平极烂,但这只是在中学棒球场上偶尔让我丢脸,而作为一个教授,这就不成为问题。健康是一个多维度问题,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可以简便计算的数字。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问题倒是很容易考察,那就是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个人而言,知道自己的生死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毕竟,如果医生给你做个检查然后说,“嗯,你还活着呢”,你肯定不满意。但是,当我们要考察一个群体的健康状况时,知道他们的生死状况就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无论是对整个人类还是某些特定群体,譬如男性或者女性,白人或者黑人,儿童或者老人,都是如此。
一个人们所熟知的衡量生命状况的方法,是去看一个新生婴儿的预期寿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经常简称预期寿命)。假设生命是有意义的,活得越久就越好,那么一般而言(尽管不是必然),活得长的人,就是健康状况更加良好的人。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的预期寿命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富裕国家的人预期寿命更长,而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预期寿命总体上一直在增长。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人类预期寿命增加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是如何实现今天的成就的。这本书不是一部健康史,也不是预期寿命史,但是,回顾过去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而只有试着去了解这一切,我们才有可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将从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人口出生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说起,来考察我们今天的现实状况,同时引入一些将会用到的概念。之后我将把视线拉回到远古,去看一下最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最后,我们会迅速将讨论内容推进至1945年。“二战”结束是一个非常好的终止讨论的时间节点,因为在“二战”之后,相关数据显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了,而人类健康故事的主线也发生了变化。
19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47.3岁,到2006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了77.9岁。图2–1按性别分别显示了美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由这张图可见,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基本贯穿20世纪始终。近一个世纪里,男性、女性的寿命都出现了明显增长,其中,男性寿命增加了28.8岁,女性寿命则增加了31.9岁。在20世纪上半叶,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下半叶,但是增长的趋势则一直延续。在过去的25年中,男性的预期寿命每5年会增加1岁,而女性的预期寿命则是每10年增加1岁。从这张图中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人类的健康状况取得了极大进步,变得越来越好。这也是本书在大部分时间里论述的主题之一。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人的预期寿命就增加了30岁,这样非凡的成就可谓是一次伟大的逃亡。除了这一主要特征外,我们还关注到图中的一些次要信息:男性与女性之间,除了在预期寿命方面有所差别,在寿命增长的速度上也不尽相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前50年的预期寿命增长特征,与“二战”后有明显不同,这又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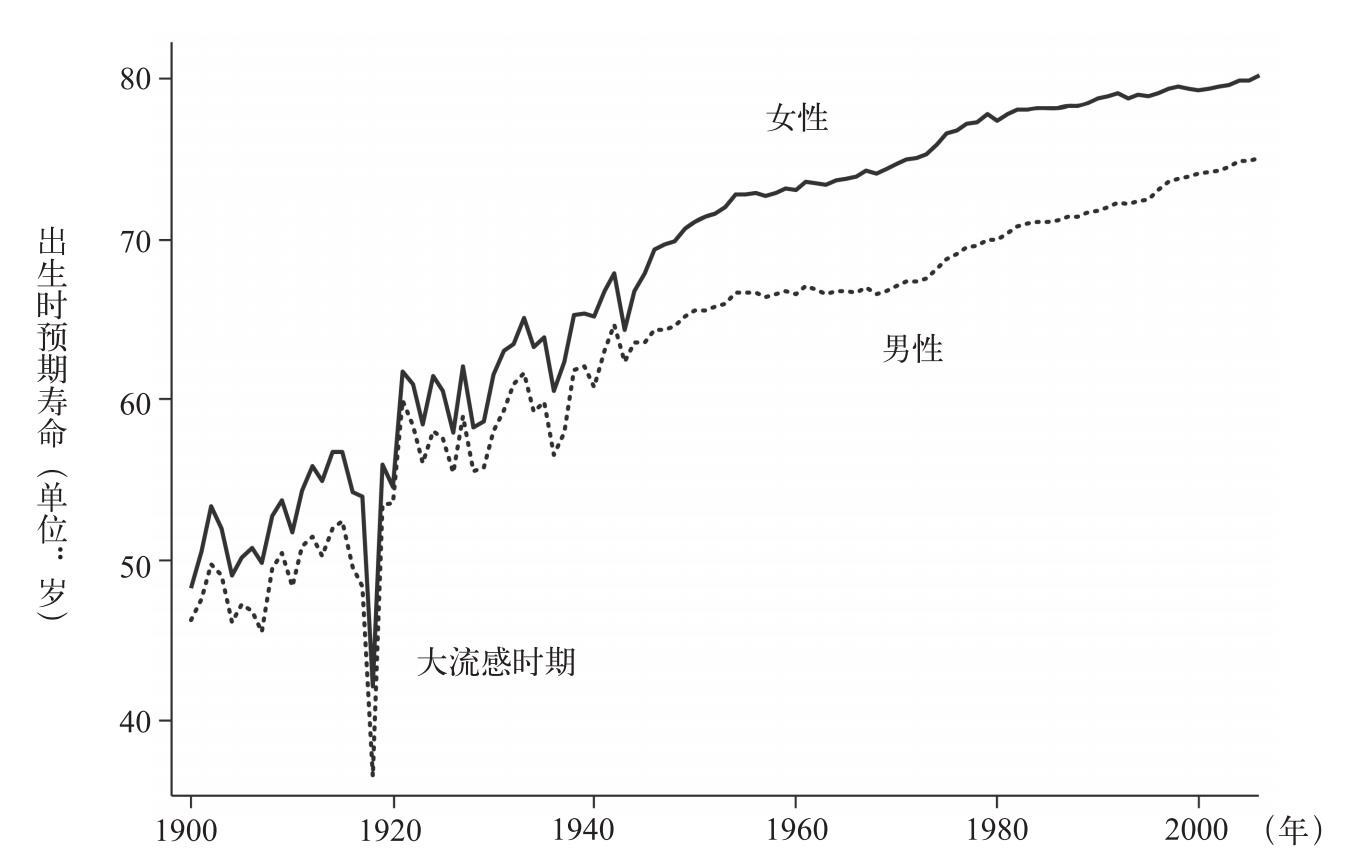
图2–1 美国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
图2–1给人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在“一战”后的大流感时期,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了一次巨幅下降。同1917年相比,1918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而到了1919年,预期寿命又从谷底反弹了15.6岁。在大流感结束之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趋势迅速恢复。当时,全世界有超过5 000万人死于大流感,其中美国人超过50万。当然,当时预期寿命的定义方法实际上夸大了大流感对新生儿童存活概率的影响。如今我们知道,这场流感其实只持续了一年,因此,只要婴儿能够活过第一年,他们就不会再遭受流感的威胁。然而,1918年,当人口学家计算预期寿命的时候,他们假设这场流感会长期持续。而到了1919年,他们就忘记了流感这回事。这种评估生命机会的方式,看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确很难找到更好的评估方法。
当一个新生儿出现在面前,需要我们去计算他能活多久时,我们需要知道他未来将会面对哪些死亡威胁,而这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人口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婴儿出生时面临的死亡风险当作未来的风险。他们假设人们在未来的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和出生时的风险一样,并以此计算出人的预期寿命。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人生每一阶段的死亡风险都突然被增大到了1918年的水平,因此,在计算这一年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时,学者所做的假设就是,这个新生儿在未来的每一年都要面对与1918年同样水平的死亡风险。如果流感永久持续,或者至少在这个孩子的整个一生中持续,那么,以上的预期寿命推算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流感只持续一两年,那大幅降低预期寿命就把这个孩子一生中的实际风险过分夸大了。当然有更好的计算寿命的方法,那就是等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有孩子都死去再进行统计。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近一个世纪才会有结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依靠预测。但是预测也有其难题,比如在1917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来年会有一场大流感。
标准的预期寿命计算,既不是等着所有人都死了再做统计,也不是做预测,而是使用时期指标。所谓时期指标指的是,将一个时期内的死亡风险假设为永远不变,然后基于此来计算预期寿命。这种计算方法上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过去的大流感时期,在今天我们考察预期寿命时,也需要面对。当我们观察图2–1,分析其中的数据,很难不认为预期寿命会继续增加而死亡风险会继续下降。这意味着我们今日的预期寿命值,可能低估了这些新生儿的寿命。今日一个女孩的预期寿命是80岁出头,然而,如果我们的健康水平继续改进,那么这个女孩能活到百岁,便是一种合理的预期。
图2–1中,1950年前的预期寿命变动幅度明显比1950年后的要大许多。大流感仅仅是造成这种大幅度变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小规模的疾病也会引起预期寿命的变动,但是没有哪一种病可以与这场大流感相提并论。在今天,传染病已经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1900年的美国,它却时刻威胁人类的生命。当时,人类死亡的前三类原因分别是流感、肺结核以及痢疾。肺结核在1923年以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到了1953年,它仍然是引起死亡的十大疾病之一。肺炎、腹泻以及麻疹等传染病,夺去了许多儿童的生命。在20世纪初期,传染病引发的儿童死亡威胁远比今日的要厉害得多。如今,死亡人口多数变成了老年人,夺走他们性命的是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而不再是传染病。这一死亡人口特征的变化,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比较富国和穷国时提到的流行病学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转变在今日的富裕国家中已然出现。
“死亡的老龄化”,是指死亡人口从儿童向老年人的转移,使得预期寿命对死亡的年度变化不再敏感。而传染病的减少,使得死亡的年度变化跟此前相比也不再显著。儿童存活率的提高,比老年人存活率的提高更能影响预期寿命的计算。一个新生儿若是能从某些致死的疾病中获救,就有机会再活很多年;而一个70岁的老人,即便被从濒临死亡的状态中救回来,也不能再活很久。这也是近几年来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也在减缓的原因。如今,婴儿的出生死亡率已经很难再降低,有降低空间的只有老年人的死亡率,而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对于预期寿命的影响非常小。
与老年人的死亡率相比,预期寿命对婴儿死亡率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是说,挽救一个孩子的性命,就比挽救一个成年人的性命更为重要或更有价值。这是基于多重因素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一方面,救活一个儿童意味着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潜在生存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一个新生儿生命的终结,也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使得许多的规划、利益、关系包括友谊等被迫终止。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曾经建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或可以根据来参加他葬礼的人数做判断,这或许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完全剔除掉年龄的影响权重。但是健康水平这样的问题,靠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机械的指标很难解决。预期寿命是一个有效的指标,它抓住了人类健康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如果我们选择预期寿命作为衡量人类幸福的一个指标,并将其作为一个社会目标,那我们实际上是接受了一种将年轻人的死亡率看得更重的道德判断。这样的判断,需要仔细考量,而绝对不能不假思索就予以采用。
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有时候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图2–1显示,在20世纪上半叶,预期寿命的增速远高于下半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1900年时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而年轻人的死亡率下降对预期寿命的影响非常大。到20世纪末,中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特征则更为明显。如果我们将预期寿命视为人口健康状况的标准,甚至将其看成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较好指标,那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美国在1950年前的表现比在1950年后的要好。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探讨的结论,但要知道,集中于预期寿命的讨论,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年轻人的死亡率放在了老年人的死亡率之前考虑。这一点必须先讨论清楚,而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穷国与富国的死亡率下降对比上。穷国的死亡率下降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而富国的死亡率下降人口则主要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使用预期寿命作为衡量指标,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水平方面,穷国正在追赶富国。然而,如果从健康状况来看,甚至是从总体的人口死亡率来看,“迎头赶上”这种说法并非事实。这不过是一种基于“预期寿命是健康水平和社会进步的最好指标”的假设。在第四章中,我们会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图2–1显示,在美国的性别预期寿命对比中,女性总是高于男性,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距的大小却并非一致。在20世纪初期,男女之间的寿命差距一直是2~3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此后男女在寿命上的差距才有所拉大。到21世纪初期,男女预期寿命的差距再次缩小至5岁左右。性别之间的这种差异,到目前仍远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整个世界范围以及整个人生时间段内的死亡风险都相对较低。甚至在出生之前,男性的死亡率也要高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要面对生育死亡的风险。在过去的20世纪,美国的生育死亡率出现了下降,这也是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造成男女寿命差异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吸烟方面的差别。吸烟会引发心脏类疾病和肺癌而导致死亡,这两种病的区别是,前者发病相对较快,而后者从接触吸烟到死亡大概需要30年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因为在年轻时就开始吸烟,男性的预期寿命增长缓慢。与女性相比,男性开始吸烟的时间一般较早。在很长的时间里,女性吸烟是为社会所不容许的,现在看起来这种对女性的不公平,反而为女性的健康做出了贡献。不过,与女性相比,男性戒烟的时间也更早。在图中折线的尾端,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速出现下降,而早在二三十年之前,男性预期寿命的增速就出现放缓迹象了。近年来,美国女性的吸烟比例也在急剧下降,与之相应,女性的肺癌发病率也出现了下降。这种情况在多年之前就在男性身上出现了。对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而言,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吸烟就成为决定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
男女之间的死亡率差距,并非是出现在美国人群中的唯一不公。2006年,非裔美国男性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比白人男性的要短6岁。在女性方面也有类似的差别,只不过差别稍微小一点,是4.1岁。同男女差异一样,这些差别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在20世纪初期,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大于15岁。这里说的非白人,包括非裔美国人但不限于这一群体。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与他们在整个世纪大多数时候所面对的不平等,譬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甚至投票与选举权的不平等遥相呼应。如此多方面的持续不平等,意味着在整体的福利方面,黑人与白人的差距要比在任何一个单一方面的差距更加突出。任何对美国黑人与白人差距的研究,都必须考察这样的一幅全景,而不能只看健康或者财富上的差别。医疗服务提供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同种族之间死亡率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却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不公平现象。死亡率差距的缩小和预期寿命的差距缩小,是整个世纪中种族不平等减弱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一个方面的差距缩小,往往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差距缩小。当然,简单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众多的差异。比如2006年,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比其他的白人长2.5岁。大逃亡发生在美国各个种族的人身上,但是不同的群体起点不同,其逃亡的速度也不相同。不平等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
尽管美国在医疗上的花费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人却不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口。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还十分相近。但在随后的20年中,英国人超过了美国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英国再次超过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差距还只有0.5岁,但到了2006年,两者之间的寿命差距就扩大到了1.5岁。瑞典与美国的差距更大,其人口预期寿命比美国的长了整整3岁。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瑞典人的预期寿命优势在不断扩大,但在有据可查的时期,瑞典人的寿命一直比美国人的长。在第四章中,我会继续讨论富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以及差距出现的原因。同美国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一样,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别。不过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相比,这种差距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预期寿命,我们需要更深入一步,考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图2–2显示的是在选定国家和时间段内,死亡率随着年龄变化的情况。图中包括了瑞典1751年的数据(瑞典的数据统计时间之早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美国1933年和2000年的数据以及荷兰2000年的数据(瑞典2000年的数据和荷兰的十分相近,但在年轻人和高龄阶段的数值略微低一点)。这些曲线显示了从刚出生到80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80岁以上的人口死亡率会稀释数据而造成曲线的不可靠,所以不在图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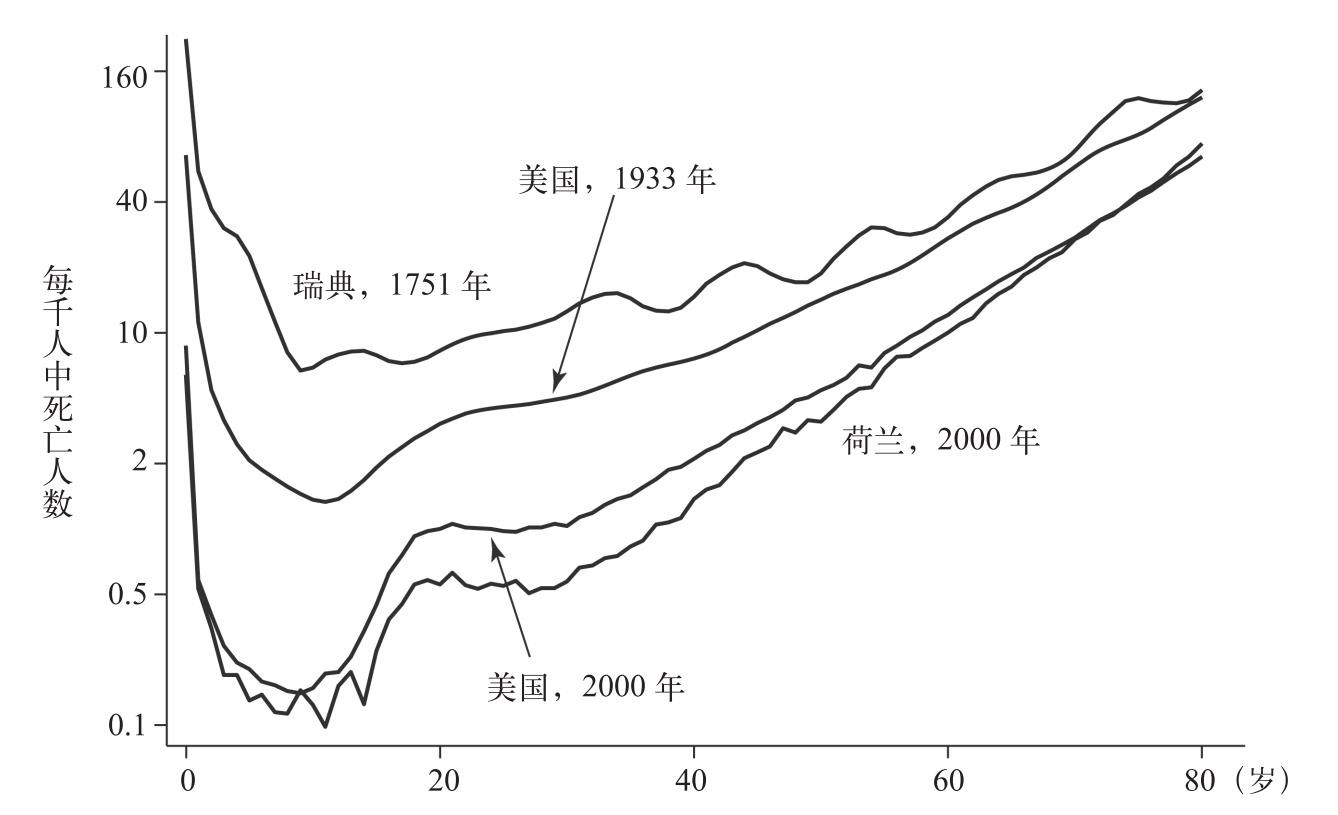
图2–2 在选定国家与时间段内,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死亡率
人口死亡率表示的是每千人中的死亡人口数。举个例子,最上面的这条线,即瑞典在1751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当时每1 000个新生儿中,超过160人没有活过1岁。而到了30岁这个阶段,每1 000个人中只有10个人没有活到31岁。本图的纵轴再次使用了对数标尺,从0.5到2,然后从10到40,每一个间隔都是以4的倍数增加。由图可见,最低的人口死亡率出现在今日荷兰10岁左右的位置,这一阶段的人口死亡率是1751年瑞典新生儿死亡率的1‰,同时只有1933年时美国10岁人口死亡率的1/10。
死亡率曲线的走势特征是,低年龄段人口死亡率较高,然后在少年早期的时候迅速下降到一个低点,之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稳步上升。这样的形态会让人想到耐克的商标。死亡风险出现在生命的最早期,然后又在老年阶段重现。我曾走访过一家妇产医院,它洗手间里的一则提示把这一点描述得极为生动。这则提示意在提醒大家要认真彻底地洗手,因为“人生最初的几天是非常关键的”。在这则提示的下方,有人紧接着胡乱涂添了这么一句:“但没有人生最后的那几天关键啊。”这个笑话主要揶揄的是医护人员对“关键”这个词的用法,但是,它的确很清楚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在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时期,人的死亡风险是最高的。
在不同的时期,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一直在变化。在1751年的瑞典,现代以来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的事情尚未发生,因此,当时新生儿的死亡风险要比一个80岁老人的高。今天,1岁之前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低于了1%,而80岁老人的死亡率则比这个数字要高出6倍还多。在18世纪及之前的数千年中,很多人在儿童时期就夭折了,在1751年的瑞典,大约有1/3的儿童活不过5岁。而在今天的瑞典和其他富裕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年纪大了才会遇到死亡问题。事实上,如今瑞典的婴儿出生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了3‰。
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死亡率的变化,意味着在一个有很多儿童死亡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活到预期寿命所宣称的那个年龄。我们经常认为,某个指标的平均值是有代表性或者典型性的,但是平均寿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本身就不准确。在18世纪晚期的瑞典,人口预期寿命低至35岁左右。这有可能让人以为真的没人能活到老年,真的没有孩子能见上他们的爷爷奶奶。这是错误的,不是事实。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可以克服童年时期的种种危险,那么其活到老年的机会是很大的。当然过去的条件不能与今日的相提并论,但是也足以保证一个人可以活到其孙子辈出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个国家有一半的孩子在出生后就死了,而另外一半都活到了50岁。这样,这个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就是25岁,但是没有人在25岁早逝。此外,在这些人活过1岁的时候,其预期寿命就变成了49岁,这就比出生时预期寿命长了24岁。另外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英国人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有时这被称作成人预期寿命)比出生时预期寿命还要高。关于这一点,稍后我还会再谈。但总体来说,记住死亡率的耐克形走势,对于理解生存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化以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等问题,至关重要。
图2–2中的耐克形曲线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死亡率也在稳步地下降。近代的曲线,总是在过去时代的曲线下方。我们无法掌握美国或者荷兰在18世纪时的相关数据,不过可以假设它们的情况和瑞典的基本类似。在1933年和2000年,人们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出现了大幅下降。与之前的年代相比,人口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这一特征在低龄段的表现最为明显。但是,也不能忘记,老年阶段的人口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在1933~2000年这段时间,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明显。对比荷兰与美国在2000年的数据,再一次证明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表现确实糟糕。在这一年,美国0岁到73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都高于荷兰。美国和荷兰的这种差距并非特例,在与其他富裕国家之间,这样的差别也同样存在。而对于活得足够长的人来说,美国的死亡率则就显得出奇的低。这或许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挽救人的性命,即便是对那些只有几年可活的人,也绝不例外。
图中底部的两条曲线,显示在2000年的美国和荷兰,20岁是一个死亡的短暂高峰。在15~34岁,人死亡的原因通常并非疾病——尽管这一时期艾滋病出现短暂的蔓延势态而抗艾药物也尚未出现——导致这一年龄段人群死亡的主要因素通常是事故、凶杀和自杀。同早期的曲线相比,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遭遇这些状况的概率比70年前更加突出,而在18世纪的瑞典,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些数据出自何处?我们是怎么知道以前的死亡率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富有国家,出生和死亡都由政府统一登记统计。孩子出生时有出生证明,而当人死之后,医生或者医院也会出具死亡证明,上面会清楚注明包括年龄、性别、死因等在内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登记系统”,包括了出生和死亡两大内容。为了保证出生与死亡记录的可靠性,生命登记系统必须完整,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都必须登记在册。为了计算死亡率,我们还需要知道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种族,这样才可以去研究死去的这部分人的相关情况。这些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自定期的人口普查。一般而言,多数国家每10年左右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不知什么原因,几乎所有的普查都是在以0或者1结尾的年份进行)。
瑞典是最早建立完整生命登记制度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获得瑞典早在18世纪的死亡率统计数据。伦敦自17世纪开始编制死亡率报表,而欧洲教堂的记事簿则更为久远。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认为,人口登记是政府而非教堂的职责,因而在马萨诸塞,1639年就有了生命登记制度。尽管到了1933年全美国才建立起完整的生命登记制度,但这仍算是政府能力的一项重要体现。没有人口出生与死亡的综合统计,整个社会对公民的基本状况就会处于全然无知的状态,而政府所要行使的各类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职能,也就无法实施。18世纪的瑞典人和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富有远见卓识,他们为好政府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图2–1中,1933年的美国预期寿命数据来自当时有生命登记制度的几个州。而世界上还有多数的国家,缺乏建立生命登记制度或者是开展人口普查的能力,对于这样的国家,人口学家采用某些技巧或者估算的方法来填补相关的空白。在很多国家,婴儿和儿童的死亡仍是普遍现象,而对这里的母亲进行调查,通常就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出生数和存活数。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了大量有价值的人口学调查和健康状况调查,这些调查为许多没有生命登记制度或者是登记制度有名无实的贫困国家收集了大量信息。(父母不为自己的孩子做出生登记,以及当孩子或成年人死亡时,依照地方习俗土葬或者火葬,这些都使得相关信息没有被录入国家数据库。)
成年人的死亡信息统计也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很多国家,即便是最好的估算也跟凭空猜测相差无几。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得到如图2–2这样完整的死亡率耐克曲线是不可能的。因为受儿童死亡率影响极大,预期寿命相对来说更好猜测,然而对于那些成人死亡率异常或者多变的国家(例如受艾滋病影响的国家),对预期寿命的估算也需要极为谨慎。正是由于种种可测不可测的原因,将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健康状况变化与富国的健康状况变化分开讨论,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而这些正是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将会讨论的内容。
今天的人口死亡率特征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的原因是什么?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何而改善?如今世界上仍然有大量人口面临着早逝的威胁,逝去的历史能够为他们的健康改进提供怎样的经验?
人类在存在于地球的近95%的时间里,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这种生活持续了几十万年。如今,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他们几乎都生活在沙漠或者极地等边际环境中。要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健康有关,这可能显得有点奇怪,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正是这种长期的狩猎采集生活,塑造了我们人类本身。人类朝着狩猎采集者的方向不断进化,身体和头脑也为了适应这种生活而不断调整。而之后人类又变成农民或者市民,过上一种现代生活,这整个过程不过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而已。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是为了适应哪些情况而自我改变,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今日人类的健康状况。
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在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而生为何而死,但是,大量的考古记录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通过研究骨骼残骸(即古病理学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的营养状况、疾病状况以及死亡原因等大量信息。也可以从残骸中估算出人的死亡年龄,这样我们也就大概了解了他们的预期寿命。在过去的200年中,人类学家一直在对现存的狩猎部落进行观察研究。不过,一些最好的证据,包括医学证据都是来自对当今人类群体的观察(因为他们与现代社会的接触,结果需要做适当的调整)。通过将现代人的相关数据与旧式部落的各项研究成果相结合,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有用数据。
饮食与运动是非常好的讨论起点。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快走以及追踪猎物等活动,他们一天要行走10~15英里。他们的饮食以水果与蔬菜为主,因为获得这些东西比狩猎要简单得多。野生的植物与今天的栽培植物不同,它们都富含大量的纤维,也就是说,古代人吃的大都是粗粮。虽然有些极其幸运的部落生活的地方有大量的动物存在,但肉类仍然十分珍贵且难以获得。与今天被驯化的动物相比,野生动物的肉脂肪含量更低。古人们所食用的植物和肉种类繁多,甚至比今日很多农业社区的食物种类还多,因此很少有缺乏微量元素的问题,更不会有因缺乏微量元素而导致的贫血等疾病。在当时,工作是一项协作活动,家人和朋友集体出动,人们需要合作才能成功地获取食物。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每年体检时医生跟我们说的:多运动,少吃肉,多吃水果和蔬菜,多吃粗粮,不要经常一个人趴在电脑前,要多和朋友出去参加活动。
尽管狩猎采集者不知道现代保健的概念,但是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们维护了自身健康。当时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女性会生育4个左右的孩子——依照如今世界上最穷国家的标准看也是很低的,并且生育间隔长,而且都是长时间母乳喂养。婴儿经常被杀或许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而母乳喂养也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因为母乳喂养会降低怀孕的概率。同时,母乳喂养也使得女性和男性一样,身体得到了大量的运动。人类排泄物对食物或者水的污染(文明的说法应该是疾病的粪口传播路径),是将疾病从一个人传染至其他人的重要途径,最终可能会引起千百万人的死亡。但在人口密度小的地方,粪口传播疾病的危险性就小得多,与此同时,很多狩猎采集部落也不会久居一地,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粪便累积而导致不可控的风险。但即便如此,在当时,还是有20%的儿童活不过第一个生日。按照现在的水平,这个比例当然有点高,但是和18~19世纪富裕国家的情况相比,这个比例也没有差多少,甚至还更好一些。与20世纪及21世纪很多贫穷国家的情况相比,也是如此。
狩猎采集者的组织方式是由他们的生存地点以及当地的环境所决定的。按我们假想,一支狩猎采集的队伍应该包含30~50个人,成员大多是亲戚,而队伍比较小,也便于人们能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然后,这支团队可能也会与其他人数更多的团队组织相联系,形成比如一个百人组织或者有时候是千人组织。在一个组织内部,所有的资源都是平等共享的,没有领导、国王,也没有首长或者是传教士等,没有人会比其他人分得更多,也不会有人指挥其他人去做事。按照一种说法,在一个组织中,任何企图把自己置于其他人之上的人都会遭到嘲讽,如果他坚持如此,那就会被杀掉。平等分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多数的群体都不会或者没有办法储存食物。如果一个狩猎者和他的朋友们成功猎获了一头猛犸象(或者一只1吨重的蜥蜴,或者一只400磅的禽类),他们会一直吃到再也吃不下去为止。他们无法保存吃剩的食物,以备无猎可食之需。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和整个群体共享这头猛犸象,然后在其他人捕获到大型猎物的时候,也就可以分得一份。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中,善于分享的个人和群体过得比不会分享的好。这样的进化过程最终把人类造就成一个以分享为信念的物种。我们今天对公平的深切关注,当公平的规范被破坏我们所生出的愤慨,或许都是源于史前共同的食物匮乏。不过,有证据显示,在史前某些地方,少量的存储也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在地球北部,社会就会显得非常不公平。
狩猎采集的社会群体是没有统治者的平等团体,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这就是天堂,是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在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是武力相见的,有时甚至要发展到战争的地步。大量的男性在战争中死去。因为没有首领,这样的群体或组织里就没有有效的法律秩序,如此一来,男人殴打女人或者是双方意见不合引起纷争等类型的内部暴力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而这也是导致成人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狩猎采集者可以免于患上一些传染病,但是其他类型的一些疾病,比如疟疾,却几乎贯彻了整个人类史。规模小的群体也不会持续遭受传染性疾病的影响,因为对于比如天花、肺结核以及麻疹等传染病,人一旦从中康复就获得了免疫能力;但是他们却要经受人畜共患疾病的困扰。人畜共患疾病的来源,多是野生动物、粪便以及各类的寄生虫。根据环境的不同,狩猎采集者的预期寿命在20~30岁。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是非常短的。但如果从西方的历史看,或者从今日穷国前几年的情况看,这个寿命也不算太短。
人们拥有的食物的丰富程度依地点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也正因此,不同的群体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群体的财富多寡以及寿命长短都会发生变化。一些骨骼证据表明,在之前,存在着食物丰富的时期:一些地方曾普遍存在体形巨大但是容易猎获的动物,比如在美国西部有水牛,在澳大利亚有大型的走禽。这些地域的这一时期,狩猎采集部落被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统称为原始的富裕社会。大型的野生动物为人类提供了丰富而平衡的饮食。与如今人工饲养的那些缺乏运动的现代禽畜相比,这些动物的脂肪含量要低90%。此外,这些大型动物可以毫不费力地被杀死。如此,生活在这些部落的人们不但物质生活水平很高,而且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但这种社会并非伊甸园,如果非要说这是伊甸园,那么,在大型易猎的动物被消灭绝迹之后,伊甸园也随之消失了。此后的人们在食物上被迫转向,植物、种子以及如啮齿类动物这样的体形更小、更难捕获的动物成为人的主要食物。发生在史前时期的这一退步,降低了人类生活的水准,儿童比此前吃到的食物更少,而同时期的骨骼证据也显示,同幸运许多的前辈们相比,这时期人们的身材变得矮小了。
史前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营养水平、休闲娱乐,以及死亡率,对于本书的主旨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生活的舒适程度是在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向前,也不能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一种处处皆如此的普遍状态。通过回顾狩猎采集者的历史我们发现,随着食物变得短缺,以及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人类的生活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更差了。这种恶化的情况发生在人类从觅食转向农耕的过程之中。现在,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生活比以前更好了(这里,我们只指代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幸运居民),但活得更长更好这种情况,却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且,到如今也仍然有很多人未能享受到这种生活。人类学者马克内森·科恩(他的《健康与文明的崛起》一书是本书的重要灵感源泉)就曾通过自己的观察而总结说:“人类19世纪与20世纪公认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比,这些成就其实很容易被摧毁。”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也发现,不平等并非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大多数时间的人类历史中并没有不平等现象,至少对于一个生活在一起、互相熟知的部落中的人来说是如此。事实上,不平等是文明赐予人类的“礼物”。科恩说:“潜在文明创造的过程,同时也造就了全体公民福祉的不平等。”人类在史前所取得的进步同近年的进步一样,都没有被平等地享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有了农业之后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话——就是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
农业的出现及发展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从它的出现到现在,大约只有1万年的时间,这同此前人类狩猎采集的时间相比,算得上短暂。通常我们会认为,“革命”意味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转变,比如工业革命和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便是这样的事件。但是,农业是使得人类的财富与健康更进一步,还是其本身是一种倒退,对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在全新世(距今11 500年)的开始阶段,地球上的人口增加,气温升高,这使得动物以及适宜生长的植物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古老生活方式已经不能再继续。和之前的广谱革命一样,人类食物从大型动物到小型动物,再到植物以及植物种子的转变,即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种植的转变,或许更应该理解为是针对觅食困难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多年之前就有论述。农业或许是遭遇食物困境之后人类的最佳选择,放弃觅食,成为农民,过艰辛的生活,这总比继续依靠越来越难觅且质量越来越差的野生植物种子生活要好得多。不过,也不能就此认为农业就是漫长的人类生活逐渐改善过程中的必需部分。古人猎捕动物,采集果实,用少量的时间就能获得野味,且享受到狩猎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投向辛劳的农业生产。莫里斯总结了萨林斯的观点,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收获的是劳苦、不平等以及战乱,那为什么农业能够替代狩猎采集?”
农业的固定特征使得食物的储存得以实现,它既可以依靠粮仓囤放,也可以以家庭驯养动物的形式进行。财产所有权的出现、牧师与统治者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以及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变化,使得农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但是,大型定居点的出现以及动物的驯化,也带来了肺结核、天花、麻疹以及破伤风等新型传染病。新石器革命似乎对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毫无贡献,相反可能还缩短了人类寿命:在低年龄段死亡的孩子数量仍然庞大,而死因主要是营养不良、细菌传播,以及新出现的疾病。此外,卫生条件难以改善,粪口传播也难以在大型稳定的社区得到控制。农业生活社区的不可移动性也限制了食物的多样性,改良作物的营养价值也多数不能与野生植物的营养价值相提并论。存储的粮食则有可能出现变质问题,从而成为其他疾病的源头。不同社区之间的贸易交换可以弥补本地食物种类的单调性,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疾病风险。“新”的疾病从原先不相往来的区域传播而来,让没有获得免疫力的本地居民受到感染。这些疾病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传播最严重的时候,整个社区甚至整个文明都可能因为某种疾病而灭亡。
没有证据表明在农业社会建立数千年之后,人类的预期寿命有所延长。在儿童死亡率提高的同时,成人死亡率下降的可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儿童死亡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幸存下来的都是适应能力变得极强的人。在农业出现、人类定居之后,女性的生育率比之前有所提高,虽然夭折的孩子也因此增多,但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世界人口数量的确增加了。社会繁荣时期,或者生产力因为创新而提高的时候,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并没有大幅增长,生育率和人口总量则因为土地承载力的增强而出现了较大增长。在经济萧条,或者出现饥荒、瘟疫等灾难的情况下,或者是人口数量多于食物供给能力时,人口数量就会下降。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均衡持续了数千年。事实上,人类觅食时代结束之时所面临的个人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在农业定居时期仍长期存在着。尽管中间有例外情况,但总体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直到最近的250年才有所变化。
当谈论进步的时候,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想到收入的增长、寿命的延长,而很容易忽略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其实也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增长。依照收益递减理论,世界上人口越多,每个人的收益就越少,这没有错,不过按此逻辑,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人均幸福水平是最高的;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社会。哲学家就此已经争论许多年了,其中,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布鲁姆认为,一旦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某个使得生命存在价值的基本生存点,那享有这种生活的人越多,说明这个世界越美好。世界总是支持更多人的全面幸福。如果真是如此,那假设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美好的(尽管这肯定有很多的限制性条件),那么从农业社会出现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时代,尽管未能实现全球性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死亡率下降,也依然应该被视作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快速前进几千年,看一下死亡率开始明显下降的时代。英国的历史人口学家安东尼·魏格礼和他的同事以教堂的记事簿为依据,重新梳理了英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历史。教堂记事簿记录了人们的出生、婚姻,以及死亡信息。魏格礼的研究只采用了这些教堂数据中的一个样本,这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人们会从一个教区搬到另外的教区;出生不久即死亡的新生儿往往不会被统计在记事簿上;父母们也常常将死去孩子的姓名用到新生孩子身上。这类教堂记录并不像生命登记制度那样完善,不过,这已经是目前所见的1750年以前所有国家中最完善的数据记录了。图2–3的折线显示的是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变化情况。图中折线明显变化的时期,往往和大的疫情有关,比如天花、黑死病以及汗热病(可能是流感,也可能是其他已经灭迹的病毒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但是总体来看,这300年间的预期寿命变化并无明显规律。
图中圆点表示在同样的300年间,英国贵族每10年的预期寿命。这些数据来自英国贵族对人口出生与死亡的详细记录,由历史人口学家T·H·霍林斯沃思在1960年收集而得。将贵族的数据同平民的数据相叠加,是社会历史学者伯纳德·哈里斯想出的方法,是他第一次画出了这样一张精彩的信息丰富的图。从1550年到大约1750年,英国公爵及其家人的预期寿命与英国总体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部分时候还会低于总体的预期寿命。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发现。通常,更富有以及地位更高的人要比穷人和地位低下者身体更为健康,这是一个被称作健康“梯度”的现象,而自古罗马以来就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但如今,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健康“梯度”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英国,至少有两个世纪,这个规律是失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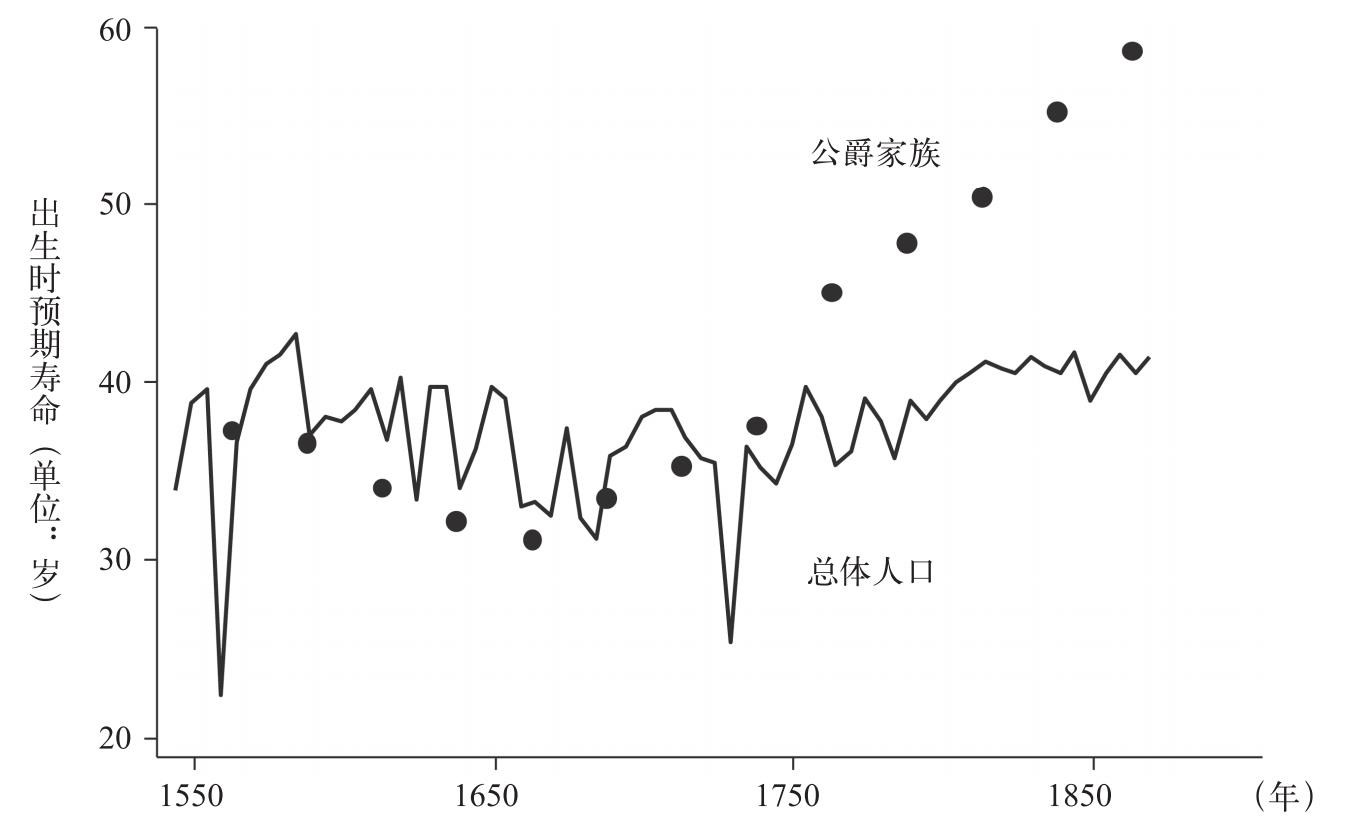
图2–3 英国总体人口与英国公爵家族的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伯纳德·哈里斯《公共健康、营养与死亡率的下降:重新审视麦基翁的观点》,《医学社会史》,2004
毫无疑问,英国贵族吃到的食物肯定要比普通人吃到的多。在16世纪的汉普顿宫,亨利八世的侍臣每天要摄入4 500~5 000卡路里的热量;亨利八世本人则过于肥胖,没有扶助连路都走不了。亨利并不是个例,在欧洲其他国家,人们摄入的热量更多。但是,更多食物,或者说,贵族们所食用的更多食物,并未使他们逃脱细菌和病毒所造成的瘟疫和天花,也未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卫生条件,使他们的孩子免于一死。与贵族阶层的这一对比显示出,在1550~1750年的英国,人的寿命更多的是受限于疾病,而非营养不良。当然,疾病与营养不良常常互相影响:当患上疾病,食物消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贵族阶层持续的高营养水平没有使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躲过传染疾病的侵袭。
1750年之后,贵族阶层的预期寿命开始与总体的人口预期寿命拉开距离,到了1850年,两者已经有了近20岁的差距。大约在1770年以后,英国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也有了向上提升的迹象。单看此图,这种提升与1550年之后数据的上下变动几乎相同,但是,在如今看来,这种向上趋势意义重大,因为在1850年之后,整体人口的预期寿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一直延续至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1850年是40岁,到了1900年,增加到了45岁,到了1950年,则接近了70岁。18世纪下半叶,贵族们不但为自身开启了向上的健康“梯度”,也为接下来预期寿命的总体进步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贵族阶层与总体人口在预期寿命上拉开差距的原因,但是有不少合理猜想。一个猜想就是当时英国开始了历史上的启蒙时代。历史学家罗伊·波特将这一时期的特征做了分析,他概括道:人们不再问“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得到的却是伤害,甚至包括一场内战。如今人们问的是“我如何才能幸福”,人们不再以遵从教会为美德,也不再“依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行使责任”,相反,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成就。运用理性,对皇室或者教会这些为社会所公认的权威发起挑战,就是追求幸福的一种表现;而在物质和健康方面找到改善自身状况的方式,也是追求快乐的方法之一。伊曼努尔·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是:“敢于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在启蒙时代,人们敢于否定公认的教条思想,而更愿意以新的技术和方式来进行实践。人们开始运用自己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使用药物和与疾病进行斗争时,敢于试用新的治疗方法。在全球化的最早阶段,多数新发明创造都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些新药物和新的治疗方法通常价格昂贵,难以获得,因此,最初几乎没有人能够用得起。
天花接种是当时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在18世纪的欧洲,天花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大城市中,天花近乎永久性存在,几乎每个孩子小时候都会得天花,而凡能战胜天花的,此后都会获得免疫力。生活在小镇和乡村的孩子则多年来一直远离这种传染病,但一旦天花流行起来,没有免疫力的人们就会被传染,大批儿童和成人都可能因此丧生。在1750年的瑞典,死亡人口中有15%是由天花所致。在1740年,伦敦每出生1 000个人,就有140人死于天花,其中绝大多数是孩子。
与天花接种不同的天花疫苗是一名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9年研制的,此后,这种疫苗被迅速与广泛地采用,并因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而获得认可。天花接种则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在1 000多年前,就在印度和中国得到运用,在非洲也得到长期试用。在欧洲,医生从天花病人身上的脓包中提取相关物质,拭在受种者的手臂皮肤之下。而在非洲和亚洲,则是将天花病人身上的干痂塞入受种者的鼻子里。接种使得受种人患上轻微的天花,但是也就此获得了免疫力。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医院部门的研究,只有1%~2%的受种人会死掉,而自己患上天花的人,有30%的死亡率。天花接种这种技术一直充满争议,一些接种的人还可能将天花传染给别人,甚至可能由此引发一场新的传染病大流行。今天,没有人再敢采用这种方法了。
天花接种引入英国,要归功于玛丽·沃特利·孟塔古夫人。孟塔古夫人是当时土耳其驻英国大使的妻子,她知道接种在土耳其被广泛接受,但是在英国上层社会,这一技术却一直未得到应用。直到1721年,英国皇室才开始接种天花。当然,在此之前,一些死囚犯和被遗弃的孤儿已经被当成小白鼠,做了接种试验,并证明接种不会带来任何不良作用。此后,天花接种就在贵族之间广泛传播。历史学者彼得·拉泽尔在他的著作中翔实记录了在此后的70多年中,接种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在最初,接种是一种费用昂贵的预防手段,并且接种者需要被隔离数周,但最终,接种变成了一项惠及普通百姓的群众运动。地方政府甚至会主动出钱给街上的乞丐接种天花,因为给他们接种的费用,比埋掉他们的尸体还要便宜。到了1800年,伦敦市内由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
在美国,接种是通过运送奴隶的船只传入的。到1760年,波士顿人就全部接受了接种,而乔治·华盛顿则给大陆军的士兵全部接种了天花。在17世纪第一个10年末,波士顿的天花大流行导致超过10%的当地人死亡,1721年,天花接种在波士顿首次得到应用,到了1750年之后,死于天花的人就非常少了。
医学史学家希拉·瑞恩·约翰逊认为,除了天花接种,18世纪晚期,其他卫生与医学的创新也相继出现。金鸡纳树皮(奎宁)首次从秘鲁引入英国,用于治疗疟疾;“圣木”愈疮木从加勒比引入,用于治疗梅毒(被认为比水银更有效但价格也更高);吐根从巴西引入,以治疗痢疾;专业的男助产士最早出现在法国,引入英国后也为富人所接受。这个时期也是公共卫生运动首次出现的时期(比如,反对饮酒的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最初的药店开始出现,而城市改造也开始兴起。我的家乡,苏格兰的爱丁堡于1765年开始兴建新城。而爱丁堡的旧城并未被毁掉,只是其中心位置那个污染严重的湖被抽干了,一座崭新的、宽敞的、健康的新城从那里向北而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于1771年出生在旧城区,他的7个兄弟姐妹中有6个在婴儿时期死去,他自己也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但司各特家里怎么也不能算是穷困的,他的母亲是一名医学教授的女儿,而父亲则是一名律师。
我们很难对医学创新之于死亡率的影响做出量化,而可能是对减少死亡最有效果的天花接种,到今天也仍然充满争议。创新带来了许多可喜的结果,同时也对尝试与犯错抱有开放的态度,它们是先进科学知识的结晶。英国贵族和皇室自17世纪末起的健康水平提升,都是拜这些创新所赐。因为这些创新价格昂贵,且未被广泛接受,所以它们最初只限于富裕人群和充分知情的人群,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导致了健康方面新的不平等。但是这些不平等也预示着总体的健康进步即将到来,因为相关的知识会被更广泛地传播,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也会越来越便宜。此外,可以覆盖全部人群的新的相关创新也应运而生,比如1799年之后出现了天花疫苗,城市卫生运动也随后逐步兴起。新知识首先导致健康的不平等,继而又推进总体福祉的提高。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许多,其中就包括19世纪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逐渐了解和接受。
如果说在18世纪,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缓慢且不平均,那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预期寿命则出现了普遍的显著增长。图2–4显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在图中,英国的数据横跨时间最长,其次是意大利,数据自1875年开始,最后是葡萄牙,数据自1940年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国的相关数据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但是它们的情况和英国较为相似,所以我们没有采用它们的数据。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数据收集较早较全面的国家,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我在此的论述将以英国为主,不过这张图其实也显示了创新扩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多次提到。英国在1850年之后,预期寿命开始增长,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葡萄牙则起步略晚。在最初的阶段,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相当大,1875年,意大利与英国的人口预期寿命相差10岁,而在1940年,葡萄牙与英国的相关差距也有10岁之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逐渐缩小,到了20世纪末,意大利的预期寿命实际上超过了英国,而葡萄牙也与之相差不远。我们知道,在18世纪,英格兰国内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出现了预期寿命差距,但与此同时,这种预期寿命的差距,也在英格兰、北欧、西北欧、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与地区,和南欧、东欧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出现。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在更多的地区出现,虽然这过程是不均衡、不平等、不完整的,但是最终,社会进步还是惠及了整个世界,而国与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也实现了缩小。总而言之,一个更好世界的出现,也同时制造出了一个有差别的世界;在一部分人取得大逃亡的同时,不平等也随之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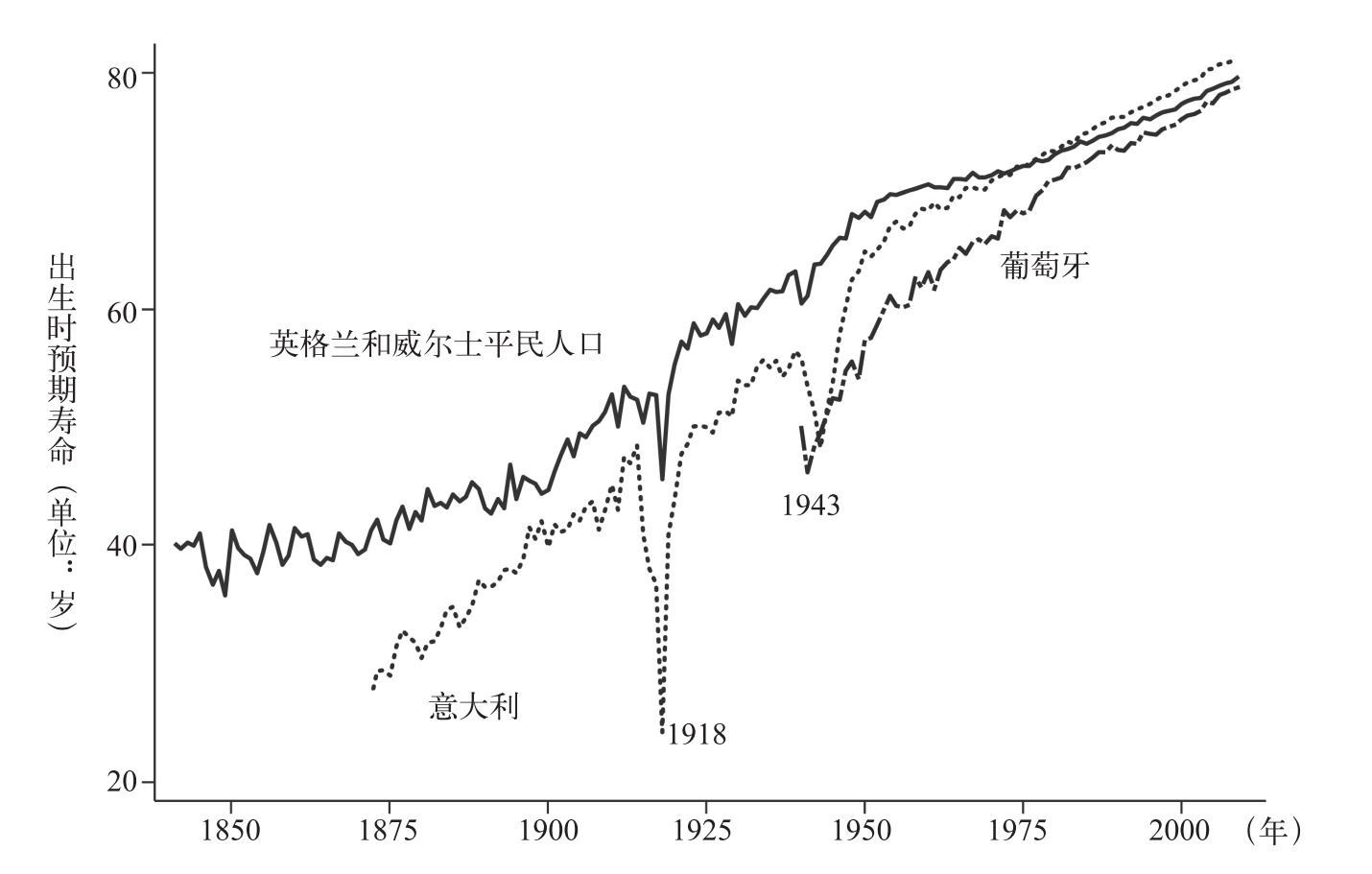
图2–4 1850年以后的预期寿命:英格兰和威尔士、意大利、葡萄牙
那么,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50年的时间里实现翻倍,从40岁变成了接近80岁?要是再想到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人口预期寿命都变化不大甚至出现下滑,那么这100多年的成就就是一场戏剧性的、快速而又令人赞叹的改变了。这样的成就,不只是人的寿命变长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相比,每一个年轻的成年人都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技能,展现激情,开拓人生,人的潜能被大大拓展,而潜在的生活幸福度也大大提高了。当然,这一些成就到今天也没有被透彻地理解,直到20世纪,才出现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
我们要就此展开讨论,预期寿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然,这里要采用的是15岁时预期寿命,而不是出生时预期寿命。15岁时预期寿命,是指人在15岁的时候,预期还能够再生活的时间。15岁时预期寿命的计算方式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并无不同,只不过计算的起点不是零岁,而是15岁。图2–5是英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与15岁时预期寿命折线图。(图中出生时预期寿命折线图同图2–4,因为我将军人的预期寿命也包括了进来,所以在此图中1918年时的预期寿命下滑幅度很大。)从此图我们可以看到,1850年,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是还能再活45年,到了1950年,人们则预计还能再活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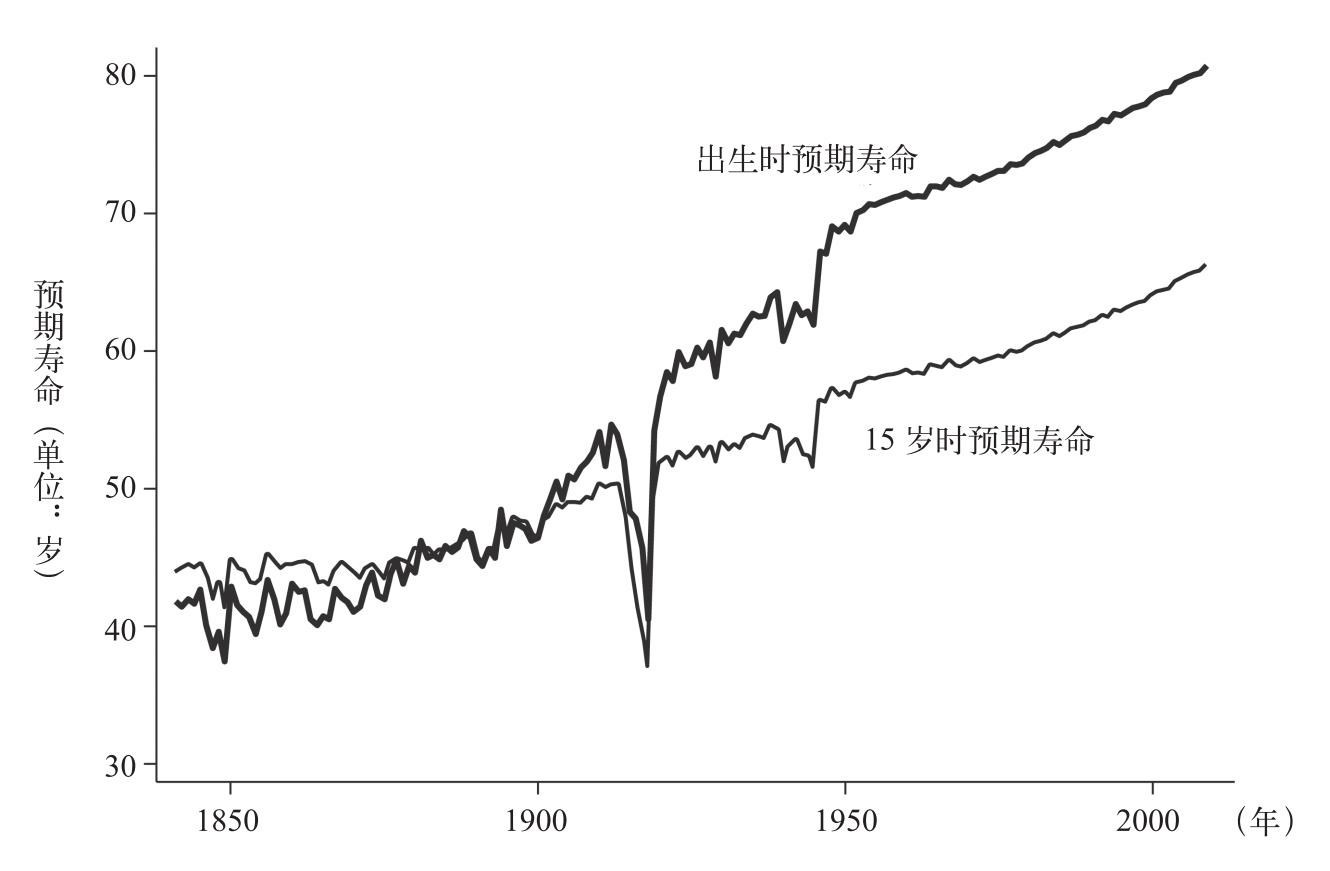
图2–5 出生时预期寿命和15岁时预期寿命(英格兰和威尔士,全部人口)
图2–5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在大约1900年以前,英国人口的成人时预期寿命要比出生时预期寿命长,即尽管已经活到15岁,预期还能活的时间却比出生时预期的还要长。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婴儿以及儿童死亡率较高,而一旦能活过童年,人的预期寿命就会出现大幅蹿升。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童年夭折的概率至少在富国已经降到极低,这样,出生时预期寿命就和成人时预期寿命拉开了差距。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15岁之前没有死去的话,那么其出生时预期寿命应该和其15岁时预期寿命正好相差15岁,而图中显示,在20世纪末期,这两个数值的差距几乎正好是15岁。在其他一些我们掌握数据的国家,类似的现象也有发生,但是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5岁时预期寿命长近10岁,而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则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5岁时预期寿命高出10~20岁。
1850~1950年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最主要是通过降低儿童死亡率来实现的。成人死亡率的下降因素,或者促使成人和儿童死亡率降低的共同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导致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因素更为关键。
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和新药物的出现,比如与抗生素、磺胺类药物、链霉素之类并没有太大关系。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在这些药物出现以前,儿童死亡率就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另外则是因为,这些新药的出现,并没有导致相关患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社会医学的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麦基翁曾经用一系列图表证实,在有效治疗方式出现之前,一系列疾病的死亡率就已经在下降了,而在这些治疗方式出现之后,疾病的死亡率几乎是以与之前同样的速率在下降。麦基翁本人也是一名医师,他认为药物其实并不是很有效(他甚至说,医生的地位越高,能起到的作用可能越小),人类健康改善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条件的优化。麦基翁是医师队伍里第一个认为自身职业对公众健康意义不大的人,他本人也因此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病症,比如贫困与匮乏对健康的影响。他认为这些才是人类健康不佳的根本原因。麦基翁认为,生活物质条件逐步改善,比如更好的饮食和更好的居住条件,比任何的卫生保健甚至医疗措施都更重要。如今,与时俱进之后的麦基翁观点,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认为健康是由医学发现和医学治疗所决定的一派,和认为健康是由人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一派,至今也没有停止争论。
显然,营养水平的提高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人所摄入的卡路里远远低于所需,儿童的生长潜力因此不能得到完全开发;成人所摄入的热量也无法保证他们身体机能健康,更无法满足他们从事高回报的体力劳动所需。人们长得瘦弱矮小,且几乎一生都保持类似身高。在整个历史中,一旦出现营养短缺,人类就会以避免长得过壮过高来自己调节适应它。长得矮小,是童年时代饮食摄入不足的一种结果,同时,矮小的身材也意味着消耗更少的热量就可以维持生存。与长得高大的人相比,身材矮小者更能适应食物短缺的生活。一个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的人想要在18世纪活下去,类似于一个不穿太空服的人想要生活在月球。总体来看,整个国家的民众没有足够的饮食使他们可以长到我们今天的身材。18世纪身材矮小的工人们被深深地困在一个营养不足的陷阱中。他们的身体条件太差,所以赚不到钱,而如果他们不工作,就没有钱吃饭。
农业革命出现之后,这个营养不足的陷阱开始崩塌。人均收入开始增加,而这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营养水平稳步改进的可能。更高的营养水平,让人们可以长得更高更壮,从而生产力也得以提升。这就开始了一种健康改进与收入增长的协同效应,两者相得益彰。当儿童身体成长所必需的营养不再缺乏时,其脑部就能发育完全,因此,这些身材高大、生活优越的人就可能变得更加聪明。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更促进了良性循环。高大强壮的人寿命更长,营养状况良好的儿童死亡率低同时也更能抵抗疾病侵袭。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和他的合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得出的一种解释。
人类的营养水平毫无疑问已经获得了改善,而人类的身体也长得更为高大、强壮、健康。但是,饮食改善并不能全部地解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仅仅关注这一点,就是低估了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视角也夸大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低估了疾病控制背后的集体协作和政治努力。理查德·伊斯特林就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当我们试图将健康水平的进步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时候,这本身就错了。在西北欧不同国家,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时间就惊人的一致,这根本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释,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起步时间非常不一样。在20世纪,心脏病防治水平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也都出现了几乎相同程度的改善。如果认为饮食本身非常重要,那为什么在1750年以前,那些吃得更多更好的英国贵族,寿命却和普通民众的差不多呢?人口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在几个欧洲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修道院里饮食条件更好的僧侣,寿命也和其他人没有差别。饮食或可以使人们远离某些类型的疾病,但绝对不是一种可以治愈一切的疗法。有可能饮食更能帮助人类抵抗细菌性疾病,但是对于病毒性疾病则无能为力。当然,关于这一点,到目前还没有定论。
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主要应归功于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对疾病的防控。这起初主要体现在卫生条件和供水质量的改善上,继而是科学知识被实践应用。并且,通过集中科学化的措施,细菌致病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了解和运用。针对一系列疾病的例行疫苗接种得到推广,而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也逐渐为大众养成。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需要公共机构的切实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的政治参与并达成共识。尽管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的确使得高成本的卫生改进项目更容易推行,但单靠市场的力量,健康改善无法实现。在个人层面,疾病的减少,尤其是儿童时期腹泻类与呼吸类传染病的减少,改善了人类的营养状况,使得人们的身高、体能以及工作能力都得到提升。食物的摄入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净营养水平。净营养的概念是指在与病魔做斗争消耗掉一部分营养后,人体所剩余的营养量。腹泻自然会导致营养流失,而在与发烧和传染病做斗争时,也会产生营养消耗。在细菌致病理论被广泛认知后,卫生状况得以改善,而这也是1850年后西北欧和英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主要原因。到了20世纪早期,这种情况也在南欧和东欧出现。“二战”以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延长了。这一方面内容,我会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
英国工业革命使得成百上千万人口从乡村涌入曼彻斯特等城市。人们进入了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新环境中,但是对于人口密集所带来的健康危险及其应对,却缺乏认知甚至完全不知所措。在乡村,即便没有对人类废弃物进行统一的规划处理,人还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不可能在城市发生。在新的城市中,人和家畜、拉车的马匹、供给牛奶的奶牛、吃垃圾食物的猪以及人的饮食同时处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工厂排出的有害废物,以及制革和屠宰等产生的公害也威胁着人的健康。饮用水常常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排泄物污染: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公共厕所的数量还不如古罗马时期的多。当饮用水水源地也被当成排泄物的处理之地时,自新石器革命以来的粪口传播链就被工业的力量放大了数倍。如此一来,城市的人口预期寿命就大大地短于了农村(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贫穷国家仍在上演)的人口预期寿命。实际上,人们是转向了健康条件恶劣的城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初期,总人口的预期寿命直到1850年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延长。这些肮脏与危险的城市,这些“黑暗、邪恶的工厂”,最终使得身处污浊而精神沮丧的人们以实际的健康状况做出了反应,于是,地方机构和公共卫生官员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公共卫生问题。
卫生运动在最初没有得到新科学的指导。事实上,当时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叫作“污秽理论”或者“瘴气理论”的疾病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闻起来臭的东西,就对健康不利。这是错误的,而且同14世纪意大利治疗黑死病所采用的那些多半无效的方法相比,这种新理论的效果也非常差。严格地看,其实有不少例子能证明这种理论有效,因为如果污染排放物能够得到安全处理,城市供水也没有发出臭气,那么人们得病的概率确实会下降。但是这种理论对于卫生问题过分重视,却对饮水供应问题关注不足。依照这种理论,伦敦的卫生机构将各户居民家中地下室里臭气熏天的小水坑抽干了,然后将废水排放进了泰晤士河,从而将霍乱病毒带入了供水的循环系统中。在若干年后的1854年,伦敦爆发了霍乱,原因就在于伦敦两个自来水厂中的一个从污水排放口的下游取水供给市民饮用。就这样,霍乱被一代人传给了另一代。另外一家主要的供水公司,在这之前不久将取水口搬到了水质更纯净的泰晤士河上游。当时的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医师,绘制了霍乱死亡分布图,从而将霍乱的传播和这家供水公司联系在了一起,并得出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水进行传播这一结论。这是公共卫生历史上最早的“自然实验”之一,在我看来,这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实验之一。不过,斯诺后来又发现这一实验结果其实是不够确定的,比如,可能一家自来水公司服务的是有钱的客户,而有钱的客户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健康的保护。这使该实验必须竭力排除其他导致这种结果的解释。
斯诺的新发现,加上德国人罗伯特·科赫和法国人路易·巴斯德后来的持续努力,使得细菌致病理论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瘴气理论拥护者的种种阻挠。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有的人暴露于疾病之下却一直没有得病?这一现象严重挑战了研究得出的因果关系和人们的认知。科赫在1883年分离出了霍乱弧菌,他指出,要想证明微生物的确是某种疾病的病因,则有四个条件需要得到满足,其中之一是,如果微生物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寄身,则此人就应该患病。不过,1892年,著名的怀疑论者,同时也是瘴气论者的马克斯·冯·佩腾科弗发现了这个理论的缺陷。他把科赫从埃及带回来的一瓶霍乱病毒当众喝了下去,然而却只有轻微的不良反应。到底他为什么能够安然无恙,原因并不清楚。当时,为了避免胃酸杀死霍乱弧菌,他还特意喝了碱性苏打水。很多病原体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会引发疾病,冯·佩腾科弗就持这样一种论调。他认为微生物必须先在土壤中腐烂,然后化为瘴气,最后通过空气传播而导致疾病。但这个理论,在1892年的汉堡霍乱大流行中被证明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同样是以易北河为水源,汉堡霍乱严重,但汉堡旁边的阿尔托纳,因为采取了水源过滤措施,并没有出现霍乱疫情。冯·佩腾科弗口吞病毒的惊世之举,是在这场瘟疫之后,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佩腾科弗的最后反抗。冯·佩腾科弗于1901年因精神抑郁而自杀身亡。
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传播以及应用,是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原因。既然孩子的生命得到拯救,那整个人类的幸福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空间。霍乱可通过污水传播,细菌会引发疾病,这些基本的知识后来都变得尽人皆知。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依此而定的政策措施就会得到立即或很快的执行:一则是我们已经看到,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知识;二则,即便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要落实相关知识和措施仍然有重重阻碍。知识或许是免费的,但要把知识变成现实,却要花大量的金钱。建设安全的饮水供应系统,要比维修污水处理厂便宜,但也耗费不菲。更何况,建设还需要工程知识以及监控措施,以确保水源不受污染。污水需要得到妥善处理,使之不能进一步污染饮用水系统;但是,对个人和企业予以监督困难重重且经常遭遇抵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力的政府和有执行力的官员。即便是在英国和美国,粪便对水的污染问题,直到20世纪也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将细菌致病理论转变成安全的水和干净的环境,需要时间,需要金钱,也需要有能力的政府。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即便到了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也依然是如此。
政治争取一向非常重要。历史学家西蒙·斯赖特就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中,淡水资源虽然到处都是,却被工厂霸占,城市居民无法饮用。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新的福利成果没有被平等地享有,承担赋税的工厂主们,不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工人们提供干净的水。斯赖特说,在工人们有了选举权之后,其政治联盟和流离失所的土地所有者们,终于起身抗争,要求建设净水公共设施。而一旦政治平衡被打破,工厂主们就见机行事了,城市之间也展开了谁比谁更卫生的宣传比赛。(我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当时也是如此。它宣称自己140英尺的海拔使它比其他疟疾横行的沼泽地区更适合年轻人居住。)当健康问题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时,不管是市政工程、卫生保障还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政治抗争也开始在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在争取水资源的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工人阶级得不到投票权时,他们就没有获得干净的水的资格,而当这前一项的不公正被消灭之后,后一项的不平等也就被消灭了。
观念的传播和实践执行需要时间,因为人们需要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富裕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学校学到认识细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洗手、消毒、合理地处置食物和废弃物来避免细菌感染。但在19世纪末期,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为大众所知,是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这些新的认识才得以广泛传播,引发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全面改变。人口学者塞缪尔·普雷斯顿与迈克尔·海恩斯指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纽约不同的族群之间,婴儿及儿童死亡率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对健康有益,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却没有相关的健康保护举措。不过,在细菌致病理论被发现之前,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和普通人子女的死亡率并无不同,而在这一理论被发现之后,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就开始下降了。在美国,当时的酒店不给客人更换床单枕套。在埃利斯岛,医生要对移民群体进行眼部检查。他们用一种纽扣钩形状的工具来检查人们是否患有沙眼这种传染性疾病,但是他们却不对工具进行消毒。这种检查其实不是要阻止传染病进入,而是在传播这种疾病。现代的例子来自印度。在印度有一种传统的接生员,其职责主要是帮助产妇解决难产等问题。一个美国医生曾亲眼看见,一位接生员的接生技巧之成熟足以使她在美国发家致富;然而这位医术高超的接生员,在从一个产妇转换到下一个产妇的过程中,却从来不洗手。
像细菌致病理论这样的科学进步,并不是单独的发现,相反,它们都是相关发现的聚合,同时,新的发现都建立在先前科学进步的基础上。没有显微镜,细菌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但是,透过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在17世纪发明的显微镜,我们只能看到高度变形的图像。色差的存在使得早期的显微镜几乎是个无用品。到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 ·杰克逊·李斯特发明了消色差显微镜,通过多个镜片的组合,解决了图像变形的问题。细菌致病理论则使得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被发现,这其中就包括炭菌热病毒、肺结核病毒以及科赫在德国实验室里发现的霍乱病毒。科赫是微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学生们继续前行,又发现了引发伤寒、白喉、破伤风以及腺鼠疫等多种疾病的微生物。紧接着,路易·巴斯德在法国发现了微生物是如何让牛奶变质的,并发明了巴氏牛奶杀菌法。巴斯德还发现消毒后的传染性微生物可以用来制作多种疫苗。(他还发明了马麦酱,要是没有这种东西,现代英国人几乎没办法生活。第六章我们会再具体讨论这项发明。)细菌致病理论还使得约瑟夫 ·杰克逊·李斯特的儿子约瑟夫·李斯特发现了手术中杀菌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和麻醉剂,现代意义上的手术就不可能出现。斯诺、科赫以及巴斯德的贡献,不但使得细菌致病理论得以创建,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是如何付诸实践从而达到维护公益目的的。
科学进步是提升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之一,细菌致病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细菌致病理论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也显示出,没有公众认可和社会的变革,新的发现和新的技术就无法发挥效力。我们也不能以为科学进步是天赐之物,可以凭空获得。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城市化后果,导致出现了很多原本在乡村中不存在的疾病,引发了对科学进步的需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工业发展导致的粪口传播,使霍乱受害者的排泄物传播到了下代人的身体之中,引发了新的霍乱;不过这也为某些学者发现细菌的人际传播路径提供了机会。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治疗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人提供治疗。但是,需求、恐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贪婪都对人类的发现与发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随其所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而这些环境也需要依赖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发展。很多在细菌理论中作用关键的微生物,现在仍处在原始状态,等待我们去发现。细菌的繁殖方式、进化手段以及毒性强弱会随着被感染者的变化而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微生物以及微生物传染疾病的方式;与此同时,也为细菌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能 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国家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运气。1945年以前,很多穷国还尚未能展开对传染性疾病的有效防控。但穷国面临的问题是,它们不应简单复制富国的道路,而应该加快步伐缩小差距。1850年时,细菌致病理论尚未建立,但100年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常识。取得这样的进步,发达国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后进国家要取得同样的进步就不能还用这么长的时间。它们必须发展得更快。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尽管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只是英国1860年时的水平,但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已经长于苏格兰人1945年时的预期寿命。过去几十年,贫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下降极快,虽然各国之间的下降幅度并不均衡,但这仍使得成百上千万的儿童得以幸存,而这也导致了人口大爆炸的出现。1950年,全球还只有25亿人口,到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目前人口大爆炸现象已近尾声)。“二战”之后,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逐步接近。自1850年起富裕国家与穷国所出现的预期寿命差距,终于在1950年之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不过,由于新的疾病出现,这一差别后来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扩大迹象。在20世纪90年代,几个艾滋病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就出现了寿命倒退,以至于它们战后所取得的寿命进步全部被抵消了。
现在,很多国家仍然存在着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在全球30多个国家里,5岁前儿童的死亡率仍然高于10%。但是,这些孩子并非死于艾滋病抑或其他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杀死他们的凶手仍然是那些在17、18世纪肆虐欧洲的病种:肠道或呼吸道传染病,或者疟疾。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但可惜的是,那些死去的孩子出生在还没有能力防控这类疾病的国家。如果他们出生在英国、加拿大、法国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肯定不会如此轻易地死去。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为何存在至今?为什么出生在埃塞俄比亚、马里或者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就会有如此大的生命风险,而出生在冰岛、日本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国度就会非常安全?在印度,虽然人口出生死亡率早就大幅下降,但是仍有大量的儿童营养不良;孩子们长得瘦弱矮小,完全与年龄不符,他们的父母也身处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群行列,其身高甚至还不及18世纪英格兰那些发育不良的成年人。贫困本是新石器革命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但印度已经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口深受贫困之苦?
“二战”之后,在联合国所定义的世界不发达地区,仍有为数众多的婴儿和儿童死去。20世纪50年代初期,超过100个国家有1/5的孩子没有活过1岁。这些国家包括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众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1960年,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有41个国家的儿童5岁前死亡率高于1/5,部分国家甚至要接近2/5。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多数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还停留在英国一两百年前的水平。但是,改变正在酝酿。
“二战”后不久,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最快速的时期到来了。人口学家戴维森·格沃特金指出,1950年左右,在牙买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以及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每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都会超过1岁,而且这种增速保持了十几年。毛里求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2~1946年的33岁增加到了1951~1953年的51.1岁;在1946年之后的7年中,斯里兰卡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4岁。当然,这样的大幅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根本上还是由于婴儿与儿童死亡率的一次性大规模下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部分归功于青霉素的应用,也与磺胺类药物的使用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病媒控制”的实现。通过化学等手段,可以消灭带病原害虫,从而达到病媒控制的效果。比如蚊子,尤其是携带疟疾病菌的疟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灭杀的。不过,随着蚊子产生抗药性,而更高效的灭蚊药DDT也因为对环境有影响而被禁用(这主要是因为之前富裕国家在农业上滥用DDT),这就使得疟疾防控所取得的成绩遭到逆转。尽管如此,病媒控制对疟疾防治仍然功不可没,而在其他方面的后续进步,诸如免疫运动的开展,则不仅足以弥补其他方法失效的损失,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专门负责儿童健康与幸福成长的机构,由于在儿童救助方面的贡献,该基金会于196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开始为欧洲的儿童接种包括肺结核、雅司病、麻风病、疟疾以及沙眼等在内的多种疫苗。除此之外,该基金会还资助了多个饮用水和卫生项目。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推行扩大免疫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推广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疫苗(百白破三联疫苗),以及麻疹、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疫苗。2000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重振1974年的扩大免疫计划。近几年免疫运动的推进出现进展减缓的迹象,这或许是因为方便接受免疫与愿意接受免疫的人群都已基本被覆盖。死亡率得以保持下降趋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口服补液疗法的出现。1973年,在孟加拉和印度的难民营中爆发了一场霍乱,一种简便的将盐和葡萄糖加入水中然后口服的疗法却治好了脱水与腹泻,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虽然这种治疗方式很廉价,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却称赞它“或许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医学进步”。急切的需求与科学上的大胆试验相结合,时常会带来治疗方式上的创新,这一点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在政府能力有限的国家,以上这些医学与技术上的进步也得到了推广应用。比如,国外来的专家或者是在国外专家指导下,相关人士都可以参与到对蚊虫的消除中,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可以利用当地的业余人员,通过短期半军事化的手段对当地群众进行疫苗预防接种。疫苗一般都价格低廉,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世界卫生组织也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拿到疫苗。他们所推行的这类通常被称作“垂直健康项目”(vertical health programs)的健康普及运动,已经成功地拯救了亿万人的生命。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属于垂直类项目,比如消灭天花的全民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世界银行、卡特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默克公司曾联合发起的消灭河盲症卫生运动以及尚在进行中的小儿麻痹症消灭运动也属于此类。
健康水平的进步不仅仅是医疗进步与公共卫生进步的结果,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等也对健康的改善大有帮助。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很多国家的教育水平也随之得以改善,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机会。我曾经对印度拉贾斯坦邦做过调查,在那里,接受调查的成年女性几乎都没有读写能力,但是,当我们考察当地女孩的上学人数时发现,在1986~1996年的10年间,印度农村女孩的入学率从43%上升到了62%。尽管有时候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但即便是很差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母亲也要比那些从未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安全意识,更为值得信赖。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大量数据证明,母亲受教育越多,孩子的生存能力和人生成就就会越多。此外,受过教育的女性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这样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照顾每个出生的孩子。低生育率对女性本身也有好处,它降低了母亲怀孕与生育的危险,同时也使得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去享受人生。
在低收入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几乎是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使得家庭收入增加,也为更好地养育子女创造了条件。经济增长也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增长,这样就为供水系统、卫生系统以及害虫根除等方面的改进创造了条件。截至2001年,在印度多数地区,超过60%的人口开始可以喝到自来水;而在20年前,能喝到自来水的人微乎其微。这不是说自来水就一定安全,但是喝自来水总比喝其他来源的水更安全。
塞缪尔·普雷斯顿是世界上对人口死亡率观察最为精确的人口学家,他在1975年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中只有不到1/4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人口寿命增长的更主要原因,在于新的生活方式、新药物的应用以及预防接种和病媒控制的推广。普雷斯顿的这一结论主要是针对他所收集数据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有不少在1945年就已经不在贫穷国家之列了。类似于第一章中图1–3那样的图表是普雷斯顿结论的主要来源。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计算,一是如果人口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的曲线保持固定,而各个国家的预期寿命随着经济增长沿着曲线移动,那预期寿命将会出现怎样的增长(收入对健康水平改善的贡献);二是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多少是来自曲线本身的向上运动(在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的条件下,其他因素对健康改善的贡献)。
近期的很多学者认为,创新与经济增长对健康改善的作用基本持平,但是正如普雷斯顿所强调的,没有理由认为这两者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那些挽救生命的重大创新,诸如抗生素、病媒控制、疫苗接种等,它们的问世既不可预见也非均衡有序。当一种医疗手段失效之后,谁也无法保证下一种就会马上出现。创新与经济增长,哪个因素对改善健康的作用更重大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边是经济增长,另一边是治疗方式的创新;一边是市场,另一边是公共卫生措施,与此同时,教育又在其中扮演着提升双方效率的角色。如果贫困国家中存在的疾病是由贫困所致,贫困消除了这些疾病就能自行消失,那么,直接的健康干预所起到的作用就可能没有经济增长来得重要。按照这种解释,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双重福音:一方面直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进健康。如果到今天,普雷斯顿的这一研究仍然有效(这个问题我稍后将进行探讨),那么单一的经济增长就不足以解释一切,要实现健康的提升就必须进行一系列健康干预。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普雷斯顿的结论与第二章的结论之间的相似性。在第二章,我们发现,欧洲与北美国家在1850~1950年间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发现了防控疾病的新手段,而经济增长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却处于从属地位。
且不论这两者之间到底谁的作用更大,人口死亡率在下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从1950~1955年至1965~1970年这15年间,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从42岁增加到了53岁。到2005~2010年时这些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又增加了13岁,达到66岁。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在增加,但是增幅要缓慢很多。图3–1显示的就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其中,最上面一条线显示的是北欧的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在这里,北欧包括海峡群岛、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以及英国。在图中,这些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最初的69岁增加到了21世纪初的79岁。这一方面的情况我将在下章进行详细讨论。再看其他地区,比如东亚(含日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则都有超过10岁的增长。这样的结果就是,如今这些地区和北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缩小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最少,但是它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图3–1显示,两者之间的差距从20世纪50年代的31.9岁缩小到了2005~2010年的26.5岁。
非洲和南亚的小部分地区(包括阿富汗)在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上还有很大空间。在艾滋病蔓延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寿命增长就比其他地方的慢,而艾滋病的出现则直接让寿命增长出现停滞,在图3–1中这一点清晰可见。近两年抗艾疗法的出现和人们的行为变化使得情况有所改观,根据联合国的预计,非洲的人口预期寿命已重新进入增长阶段。不过,艾滋病感染情况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的确出现了寿命倒退到“二战”之前的情况。像博茨瓦纳这样的国家,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经济的成功曾使其人口预期寿命从48岁增加到64岁,然而在2000~2005年,由于艾滋病肆虐,该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到了49岁。津巴布韦的情况更糟糕,这个有着非洲最差政府和最差经济的国家,在2005~2010年的人口预期寿命比1950~1955年的还要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艾滋病在全世界已经造成了3 400万人口的死亡。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疾病大流行显然不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在1918~1919年的流感大蔓延之后,疾病大流行的情况依然在出现,而且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大规模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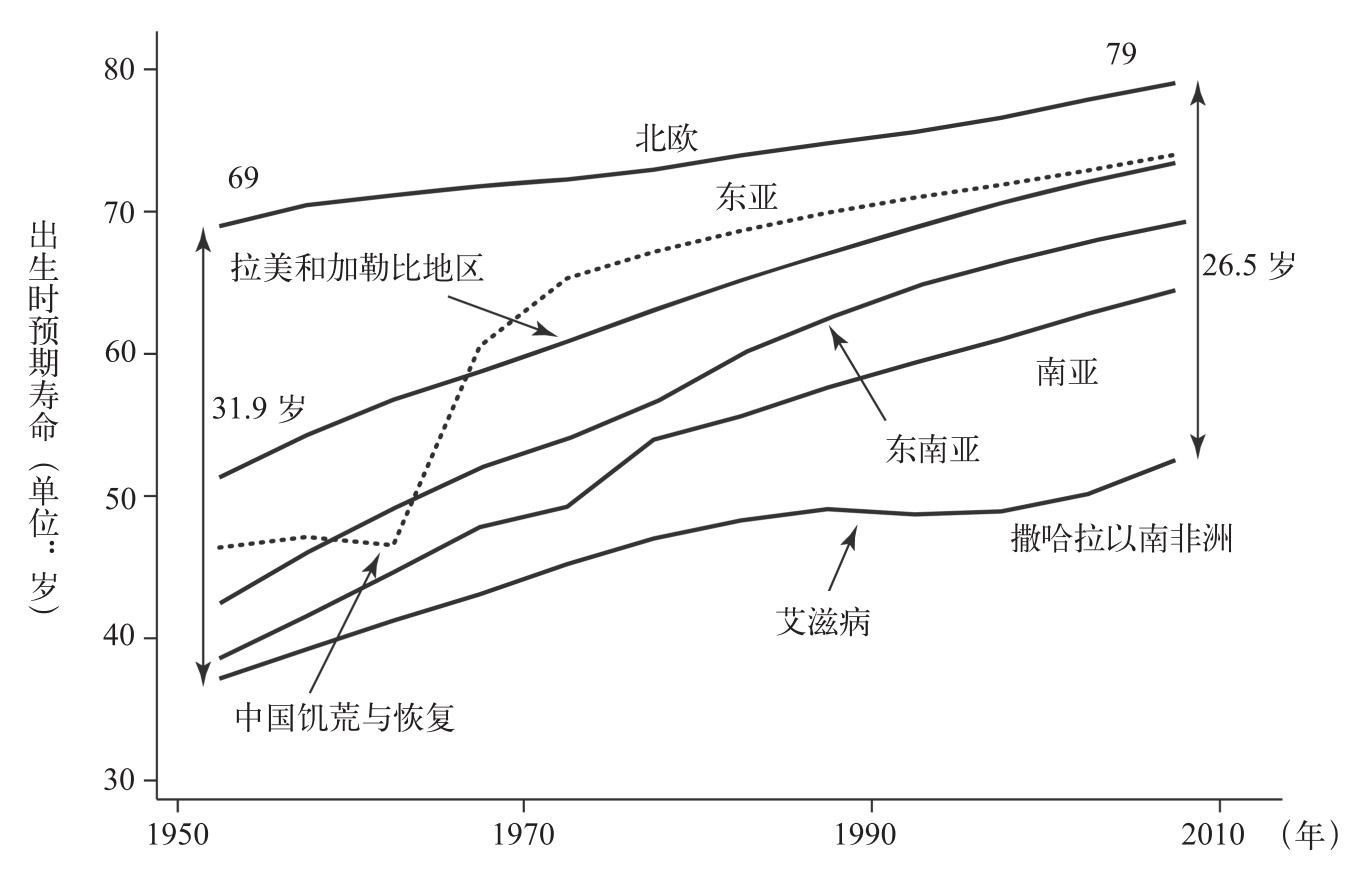
图3–1 1950年以来世界各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
没有人知道艾滋病疫情是怎么出现的,但这并不奇怪,就像中国1958~1961年间出现的粮食饥荒,原因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关于这场饥荒的起源,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做过讨论,而饥荒的影响则可以在本章图3–1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后很快会谈到中国,实际上,中国一党执政的模式有时候会很有效,因为它可以强力推进执行某些公共卫生政策,而如果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这些政策措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坏的一方面是,这种体制也不能阻止一项错误政策的执行,哪怕这项措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情形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并非西方式民主体制,但是政策执行非常有效;而印度是西方式民主体制,却经常无法有效地执行各项政策措施。不过,印度在英国统治时期经常出现饥荒,但是独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艾滋病和中国的大饥荒导致了人口寿命的倒退,但图3–1证明,同半个世纪前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们还是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机会。那么,今天的情况具体有哪些改善,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一下世界各地人的死亡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死亡原因也各异,同时考虑在现有条件下,如何避免那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媒体经常披露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称某些人是死于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相反,如果人还是死于某些古老的疾病,那我们就应该问问,为何在已经有治疗方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虽然我们肯定需要新的、更好的治疗手段,但真实的情况是,现如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儿童死于那些我们早已能防控的疾病。
表3–1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人口死亡率水平数据,其中不少数据都是估测,因此细节可能不可靠,但是这张表所显示的全景还是足够可靠的。表中,第二栏是世界整体的人口死亡率情况,第三栏和第四栏分别是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关情况。按收入进行划分的依据来自世界银行。以收入为标准,世行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类。在这张表里,我只选取了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类别,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突出世界最穷国和最富国之间的死亡率差距。低收入国家共有35个,其中27个来自非洲,其他8个分别是阿富汗、孟加拉、柬埔寨、海地、缅甸、尼泊尔、朝鲜和塔吉克斯坦。印度已经不在低收入国家之列。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主要来自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国家,还有日本、一些石油产出国以及为数不少的岛屿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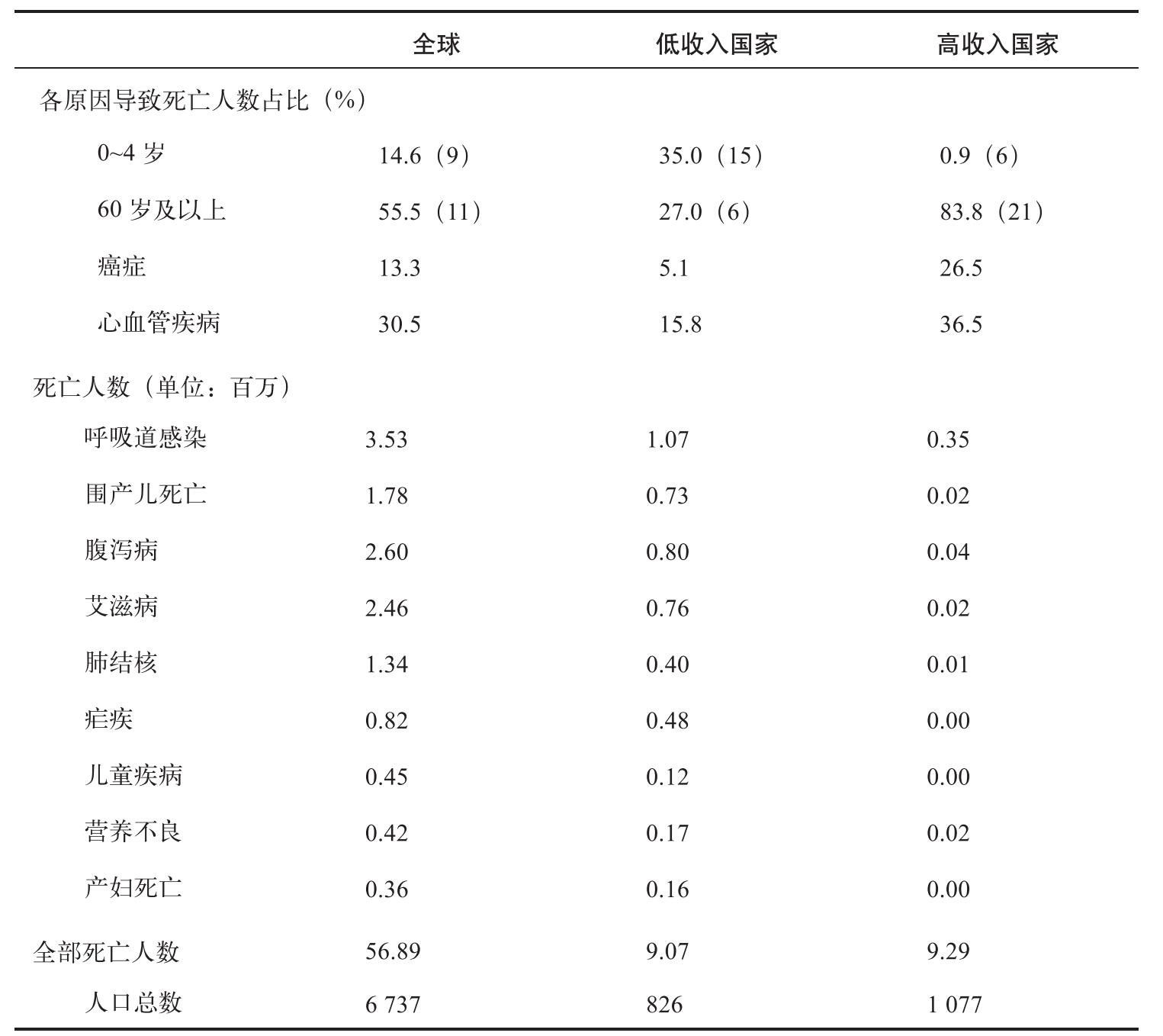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数据库,2013年2月3日
表3–1的最上面部分显示的是儿童与老年人的死亡比例,此外,这里还显示了两种最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比例。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数据,包含心脏疾病和血管疾病两大方面,也就是说既包括心脏病也包括中风。第二栏的数值是全球的总体相关数据,第三、第四栏分别是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数据。下面的数据是对死亡人数的简单统计,统计项目主要是那些在低收入国家导致人口死亡的各类疾病。
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每个年龄段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的底部则显示了每个地区的总人口数量。需要注意的是,占世界总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主要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在本表中是没有被体现的。在表的第一部分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实需要注意,那就是数据表明,低收入国家儿童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儿童人口比例。贫穷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更高,当人口增长时,就意味着年轻人更多,而整体的人口年龄也就会更年轻。在不少富裕国家,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群体已经进入老年,这使得表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在低收入国家,0~4岁人口的数量是60岁以上人口的两倍多;在高收入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则是儿童数量的3倍多。所以,即便是这两类国家在健康方面承受着同等风险,它们的人口结构也决定了穷国儿童的死亡人数会更多,而在富国,老年人死亡的人数会更多。
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婴儿与儿童占总体死亡人口的比例是15%,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的比例则超过50%。不过,富国和穷国各自的身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贫穷国家,死亡人口中超过1/3的是5岁以下的孩子,老年人只有不到1/3。而在富裕国家,死亡人口中超过80%都是老年人,儿童占死亡人口的比例则极低。因为在富裕国家,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健康长大成人,正常变老,自然死亡。出现这种差别,富裕国家老年人比例本身较高是一个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差异。比如,穷国儿童人口的死亡率也比富国的高。流行病学转变是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流行病学转变是指,随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其国民的死亡年龄也会随之延后。而人口的死亡年龄在从儿童期逐渐转向老年阶段的同时,其死亡的原因也随之从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了慢性病为主。当低收入国家转为高收入国家以后,死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口比例会增加3倍。换言之,就是老年人主要死于慢性病,而儿童主要死于传染病。
现如今,贫穷国家人口的最主要致命疾病,仍然是曾经在富裕国家肆虐的传染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称的“儿童疾病”: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这几类疾病每年仍会造成近800万人死亡。其他导致穷国人口死亡的因素还包括疟疾、艾滋病(目前仍未有理想的治疗方法)、围产儿死亡、产妇难产死亡、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主要是缺乏食物而导致的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和贫血(饮食中铁元素的摄入不足,素食主义者经常出现此种情况)。富裕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除了每年有35万老年人会死于肺炎外,几乎没有人是因为以上这些疾病而死的。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富国儿童死于痢疾、肺炎以及肺结核等病的风险已大大降低。对于富国而言,疟疾一直到“二战”之后还是一些国家的麻烦,但如今这类风险已经消失;但是在穷国,疟疾却依然是夺走儿童生命的最主要原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使用以及性行为方式的改变,减少了艾滋病的致死率。全面的儿童免疫接种也使得儿童疾病基本被消灭。对产妇产前与产后的精心护理,使得围产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都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在富裕国家,几乎没有人会因为食物短缺而死,贫血也很容易被发觉,缺乏微量元素诸如铁之类的情况,也基本上不会大面积出现。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一个在穷国死去的孩子,如果是生在富国可能就不会死去,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富裕国家,相关的医疗知识可谓唾手可得,并且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生命;但为什么在贫穷国家,这些医疗知识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运用?对于这些问题,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是“贫穷”。实际上,我在表3–1中采取“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分类方式,就说明了收入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历史的语境中,我们将痢疾、呼吸道疾病、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等视为“贫困病”,而将癌症、心脏病和中风视为“富贵病”。在前一章,通过对18世纪与19世纪的追溯我们也发现,收入的的确确扮演了重要角色,有钱人一般能够获得身体所必需的食物,而经济发展也会为病媒控制、卫生条件与饮水条件的改善以及医院诊所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即便如此,认为贫困是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这种说法仍然是极不妥当的,不仅如此,如果过多地关注贫穷与收入的关系,甚至还会产生误导,使我们忘记什么才是最需要去做的,以及谁应该去做。
在这里,中国和印度再次成为值得研究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印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而分别是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处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但是,这些年它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这两个国家,因此,认真去了解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非常重要。图3–2显示的就是在过去的55年,中印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图中右侧的纵轴表示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对数标尺表示。从图中可见,中印两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取得了持续增长,其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相比而言,印度在图中的前40年一直增长缓慢,直到1990年之后,经济增长才开始加速,尤其是在图中最后的几年,表现最为突出。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得益于经济改革措施。在1970年之后,中国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鼓舞;印度在1990年之后取消了很多英国殖民时期的沉疴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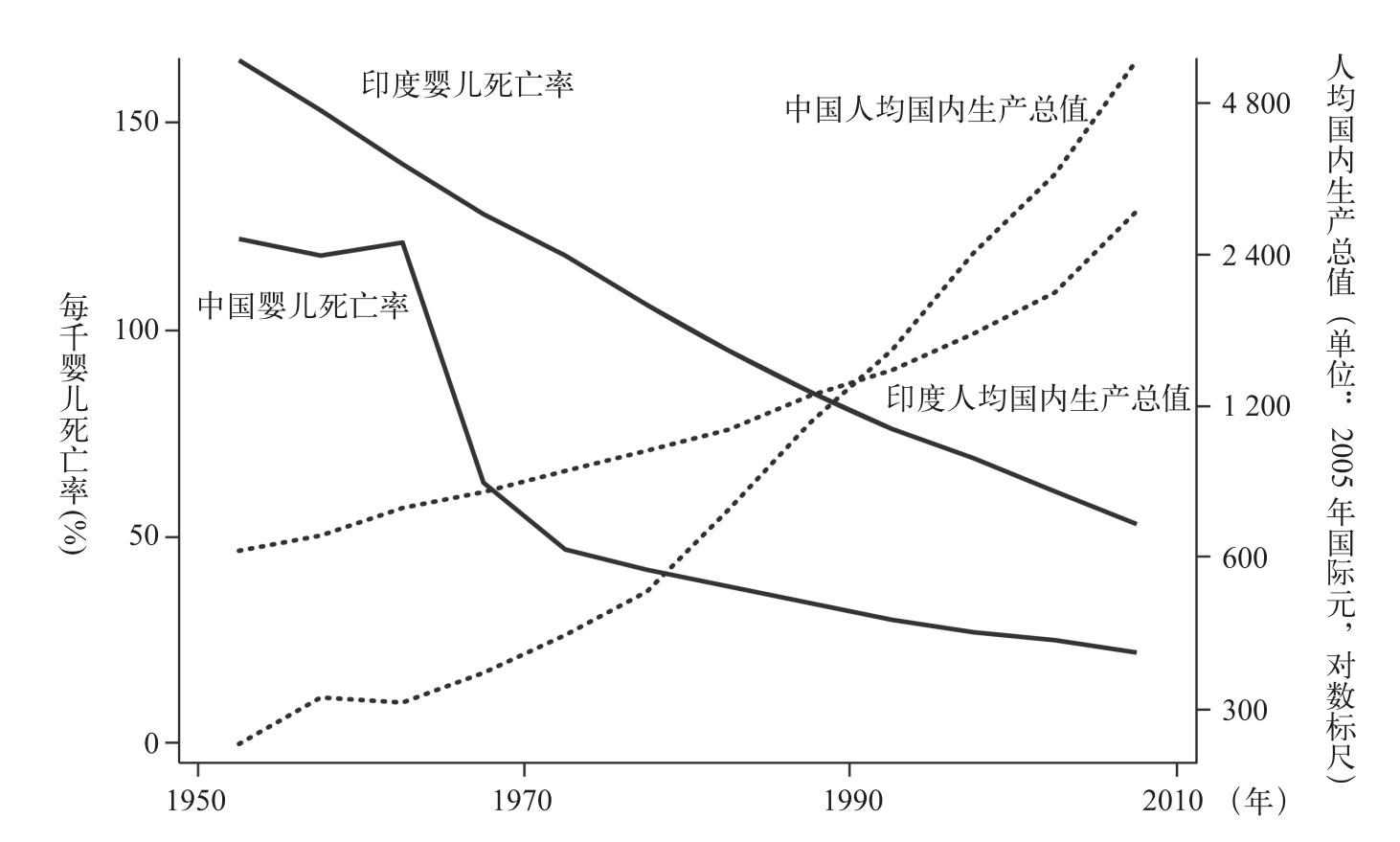
图3–2 中国与印度的婴儿死亡率与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和印度逐渐摆脱贫困,两国的婴儿死亡率也开始下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0~4岁儿童死亡率指标上,因此在图中我没有对这一指标特别加以展示。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导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一度停滞。在当时,全国有1/3的新生儿童死亡(因为此图显示的是5年平均值,因此饥荒的影响在图中表现不明显)。但是这一事件之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就开始出现急速下降,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左右。在1970年之后,婴儿死亡率仍然在下降,但速度变得缓慢很多。如果认为婴儿死亡是贫困的结果,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儿童的死亡率就应该相应下降,但是中国的例子却与此相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中国政府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所有的资源就从其他地方转移集中到创造财富这个目标上。公共卫生和健康医疗上的资源投入也在被转移的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原本从事蚊虫防控的人也因此转身为农民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但在此之前,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确实投入了巨力。一位英国医生把他1950~1960年这段时期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写成了书,书的名字就叫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Away with All Pests )。但是在推行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减弱至几近于无。当然这不是说改革不好,毕竟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事实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会带来健康水平的自动改善。在中国,政策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从结果上看,中国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方面的发展和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交换。
和中国相比,印度的表现总是慢一拍,也更不起眼。印度的经济增长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慢,而改革之后的表现也不够惊艳。此前,印度人均收入要高于中国人均收入,但是在21世纪初,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不及中国的一半(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两者的对比数据似乎不够准确)。印度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一直较为平稳,也没有和经济增长速度完全同步。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每1 000个新生儿中有165个死亡,到了2005~2010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了52个。这一下降的绝对数值高于中国的同比数值。中国同期的千人死亡绝对数是从122降低到了22,从数字看,出生在印度还是比出生在中国危险。不过,虽然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很大,但同中国相比,印度在健康方面的表现并不太逊色。此外,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德雷兹和阿马蒂亚·森就曾指出,综合来看,南亚地区的表现实际上要比中国好。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各有其特色的国家,我们不能说在这两个国家被证明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必然适用,所以,在非洲或者其他比今日中国和印度更穷苦的国家,经济发展未必不是其人口健康水平改善的主因。不过,鲜有证据能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它的婴儿或者儿童死亡率也会下降得越快。图3–3显示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没有关系。为了得到公允的结论,我这里只看长期的变化。一两年的经济大发展恐怕不会对类似于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这样的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大宗商品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扬,或许能让一部分人发财或者让政府增收,然而却不会对总体的经济繁荣产生影响。但如果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几十年,那么如果它真的有效用,其影响力就会逐步显现出来。我们现有的数据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过这张图还是显示出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与死亡率下降的情况。在图中,每个国家的数据考察周期最少是15年,平均周期是42年,而最长的时间周期是1950~2005年,即55年。图中纵轴表示的是死亡率的年度下降数值,因此,数值越大说明情况越好。因为婴儿死亡率是以每千人的死亡数来计算,所以,在纵轴上的数字2(如印度所处的数值)就表示在数据覆盖的这段时间内(印度的数据时间跨度为55年),印度的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乘以55,即每千人中死亡的人数减少了110人。富裕国家也在图中出现,但是由于它们此前的婴儿死亡率就很低,因此在后来的这几十年内,其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在图3–3中,它们都集中于底部中心区域的位置,可以说,即便把这些国家的数据都排除在外,关于婴儿死亡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结论也不会太受影响。
图3–3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经济发展和死亡率下降呈正相关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出现这种印象只不过是因为图中圆点的大小与人口规模成正比。而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是中国、印度和印尼三国。这三个人口大国恰好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其婴儿死亡率下降也要快于平均水平。但是,既然我们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关系,那我们就不能被人口规模大小所干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婴儿死亡率下降也更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对每个国家平等视之,不能区别对待。从这一思路出发,并在给予了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经济发展和婴儿死亡率高低之间并无关联。至少从图3–3的这些历史数据来看,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死亡下降率。在图3–3可以发现很多相关的例子。从1960年到2009年,海地的经济实际上一直在萎缩,但是它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得比中国和印度还快,这一点非常让人敬佩。在我们的数据中,总共有16个国家的经济比之前下降了,然而它们的婴儿平均死亡下降率是1.5%,比177个国家总的婴儿平均死亡率下降幅度还要大。这显然说明,即便没有经济增长,婴儿死亡率也仍然可以出现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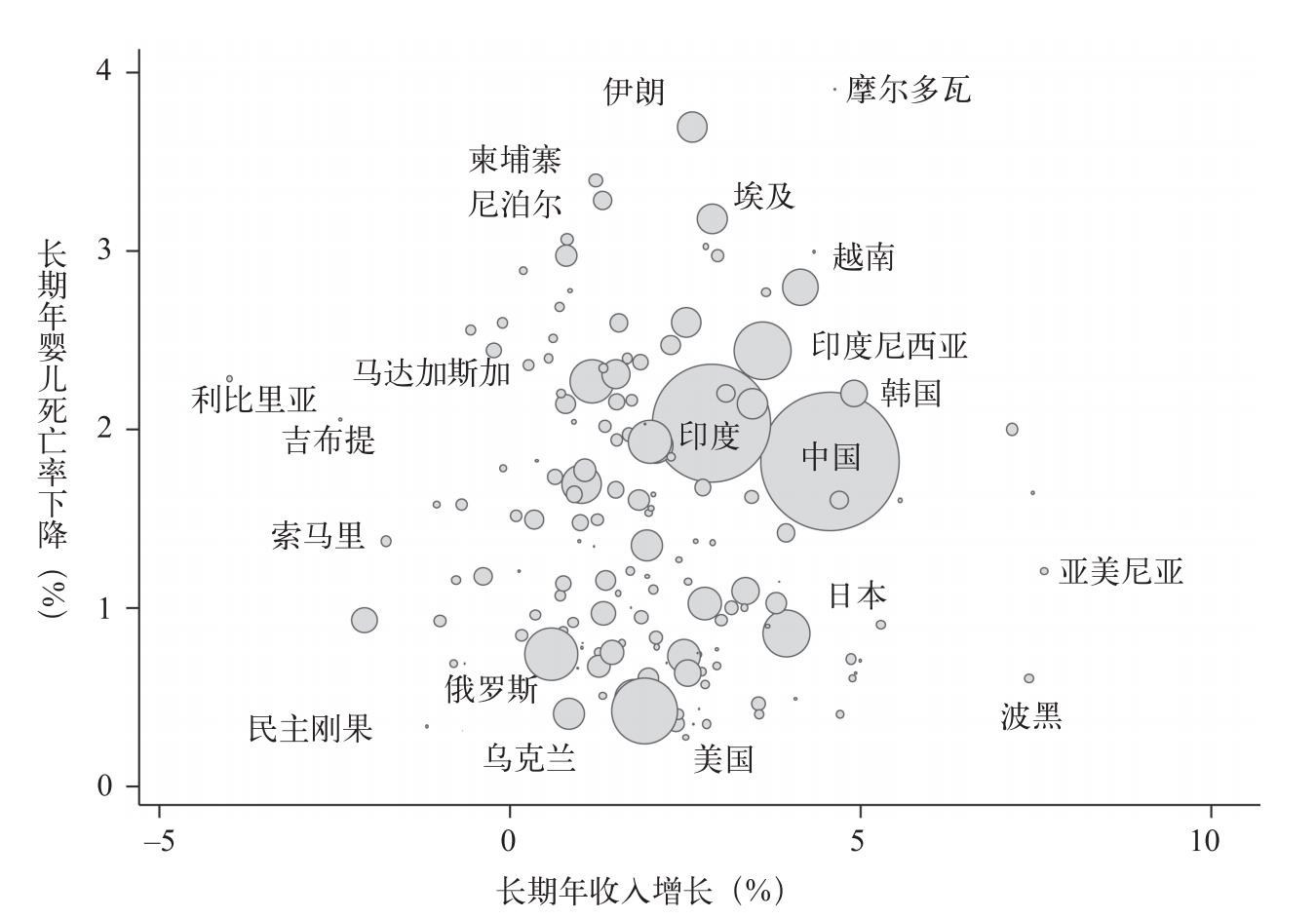
图3–3 1950年以来婴儿死亡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下降毫无直接关联这样的结论会让不少人吃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诸如疾病防控这样的因素对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可能更大,但要说经济增长对死亡率下降毫无影响,还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确,有理由认为图3–3可能是在误导我们,因为它忽视了婴儿死亡率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反向效应。当本来会死去的孩子被救活,进而人口数量增加后,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可能会出现下降,或者至少比之前增长得慢。当然,这些新增的儿童人口最终会成长为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年人,因此,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就越穷的想法也是毫无根据或证据的。但即便这样,在儿童死亡率下降的最初几年,由于新增人口主要是儿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时间,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人均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这种效应与人均收入走高对儿童死亡率的积极影响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能会将后者的积极影响全部抵消,从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死亡率之间缺乏关联性。
不过,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观点。的确,婴儿死亡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富裕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本已经很低,因此就不会出现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口也只会低增长。穷国的婴儿死亡率则会出现大幅下降,人口增长也会非常迅速。但是在穷国内部,或者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率却没有必然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生育率足以发生变化。在图3–3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最穷的国家,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联,而这种无关联现象,用死亡率下降与人口增加之间的模糊关系是不足以解释的。
如果贫困不是穷国儿童死亡的原因,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死亡的自动减少,那么,在大多数疾病已经可以被现有医疗知识与科学知识防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儿童死亡?
要回答这些问题,表3–1中的人口死亡具体原因列表或许有所帮助。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每一种致死疾病的防控处理方式也需要具体考量。肺结核、疟疾、痢疾以及下呼吸道感染等疾病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但总体上,它们的防控都需要更好地预防害虫传播疾病,需要更干净的水,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要实现这些条件,各个部门的协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做到协同,就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单纯的医生病人一对一医疗体系,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控没有效果。尽管这样的系统也可以发挥些许作用,但是本质上这些疾病的防控属于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私人健康问题。表上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尽管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控有所帮助,但仅靠这一点完全不够。
儿童患病导致的死亡、围产儿死亡以及产妇死亡,都可以通过产前与产后的护理得到避免。比如,我们可以在产妇生育前后给予生育和喂养指导;提供健康卫生设施用于处理急诊和并发症;医院和护理人员可以在儿童接种的疫苗失效时予以提醒,对父母进行相关指导,以确保孩子能健康成长。在贫困国家,孩子断奶后的这段时间特别危险,因为母乳是营养相对丰富、全面且安全的饮食,而断奶之后,孩子的饮食就可能出现营养不全面甚至不安全的情况。受过教育的妈妈可以自己去解决相关问题,医生、护士和相关人员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对于这一类致命疾病的防控,医生病人一对一的医疗体系非常有效。但是,很多国家在这个体系上却投入甚少。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它们在私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体系上的全部投入,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00美元左右,这样的数额是沧海一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世界银行曾统计过2010年的数据,发现按2005年的美元价格调整后,津巴布韦在每个国民身上的医疗费用投入是90美元,塞内加尔是108美元,尼日利亚是124美元,莫桑比克则只有49美元。相比之下,英国在其每个国民身上的医疗投入是3 470美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8 362美元。
国民的健康情况如此糟糕,这些贫困国家的政府为何还投入这么少?而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公民为何没有转向私立医疗?外国援助对全球健康某些方面的改善作用重大,那么它们的作用到底是如何体现?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改善公民的健康和生活状况方面,政府并非总是积极的行动者。即便是在民主体制的国家,政客和政府也经常各怀心思,即便大家公认在健康问题方面有亟须改善之处,他们最终也会在行动方面产生激烈的分歧。更何况,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于非民主状态。还有一类国家也没有为保障国民利益做出实际的行动:这些国家要么是因为环境所迫,比如在现阶段把重点都放在提高国民收入上;要么是因为在相关方面宪法和法律缺乏约束力。独裁国家和军事政权显然具有这些特质,另外,一些以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国家也在此列。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其政府依靠出售矿产和石油等资源就可以运行得很好,因此无须向民众伸手要钱。既然在金钱问题上不受制于民,这些国家的政府自然也就可以维持一种漠视普通民众健康福祉的体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经常出现在非洲:不少外国机构给当地的贫穷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然而却无法让这些政府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虽然出发点向善,然而这些援助提供者却只能眼看着这样的情况发生。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一章会详细阐述。
但不能让政府承担所有的罪名。在一些地方,人们似乎不觉得自己的健康水平有提升的空间,同时对政府能起到的作用也不抱期望。盖洛普咨询公司曾经在非洲就政府最应该关注什么展开定期调查,结果发现,健康并不是那里的人们特别重视的事项,其受关注度远不如减少贫困或者提供就业岗位等话题。那些以创造就业为工作重心的政府,哪怕只是在臃肿的公务员体系内增加些毫无用处的就业岗位,也会更得到选民的认可。在我们曾工作过的印度拉贾斯坦邦乌代布尔县,我们发现,虽然人们都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让·德雷兹称之为“疾病的海洋”),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这一点和财富、房产或消费品截然不同。
在非洲,人是和微生物一同进化的,到如今,这两者仍然共存。换句话说,在整个的非洲历史中,疾病一直伴随人的左右。更宽泛地看,人类逃脱疾病和早逝的困扰也只是近来才在世界各地出现。尽管如此,世界上仍然有为数众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逃脱这些疾病以及早逝的困扰,也没有认识到好的医疗保障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盖洛普的世界调查经常发现,尽管客观的健康水平差距巨大,但贫穷国家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裕国家的不相上下。尽管有的国家经济贫弱,医疗支出微不足道,民众却对国家现有的保健医疗系统信心十足。与之相反,美国人在医疗上花钱无数,却对自己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极度缺乏信心。一项研究显示,在医疗信心排名上,美国在被调查的120个国家中排名第88位,这个名次只比塞拉利昂高三个位次,比古巴、印度以及越南的位次都要低。
在很多国家,最丑陋的事情莫过于医务人员频繁擅离职守。通过随机抽查我们发现,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只有一半的小型诊所正常开门营业。大型的医疗机构虽然开门,医务人员却经常消极怠工。世界银行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很多国家——尽管不是全部——缺勤是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待遇偏低。在某些情况下,工作人员和雇主之间似乎有一种隐形的契约:政府给他们象征性的薪酬,而他们也就提供象征性的服务。不过,收入偏低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原因。当人们对健康没有过多期待的时候,缺勤旷工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发生。在拉贾斯坦邦,即便是一个护士几个月不现身,病人有时候也会无动于衷。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样的医疗水平就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好水平了。但也并非处处如此,比如印度以草根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而闻名的喀拉拉邦,因为一家诊所未能开业,那里爆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缺勤现象在这个地方非常少见,而且人们也希望医疗诊所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将拉贾斯坦邦人的标准稍稍向喀拉拉邦人的靠拢一下,那大部分的医疗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私人医疗往往会在穷国发展得一片繁荣,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常常可以填补公立医疗保障的空白或者弥补它们的不足。但是私人服务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私人医生并非训练有素,他们可能并不了解病人的真正需求。购买医疗服务和饿了之后购买食物填饱肚子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把车送到汽修厂维修。在这里,给你提供服务的人实际上必须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这些私人医生,只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或者更贵的医疗服务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不会管病人是否真的需要,而只要病人提出要求,就给予满足。比如在印度,只要病人对抗生素有需求,私立医院的医生马上就会开给病人。医生开出这样的处方,既让病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让病人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病会好得更快。静脉注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医疗服务人员会强烈建议病人接受静脉注射——这就如同在美国,医生经常会冷血地建议病人做全身扫描或者是前列腺癌的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一样。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生则不会因为病人想要抗生素或者静脉注射就开出这样的处方。这是好事,但不好的事情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又经常因为没有时间给病人做细致检查而疏忽了病人的真正需求。所以,选择公立还是私立,经常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当然,至少从短期来看,去私立医院可能会让病人有一种得到了更好救治的感觉。
如果公共医疗系统值得信任,或者私人部门的医疗服务得到合理的监管,那么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就不会出现。但是在很多国家,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得到落实。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对医疗的监管也是最困难、最富有争议、最易受到政治指控的政府职能之一。在拉贾斯坦邦,我们所见到的私立诊所医生,多半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郎中,有不少所谓的医生,实际上连高中文凭都没有。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的双重失败,其根源在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孱弱。这样的政府,既无法提供医疗保障,又不能对私人的医疗保障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控。
钱也是一个问题。像印度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若没有比现在更大的医疗支出投入,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也不难想象,更贵的医疗系统未必更好,它只不过是让那些惯于缺勤旷工的医生拿到更多的钱罢了。如果没有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又缺乏能力强大的政府,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能力强大的政府?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聘用训练有素的官员,建立良好的数据统计制度,同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二 战”之后,贫穷国家的人民开始享受到富裕国家人民早已拥有的健康水平。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使得传染病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但是,科学以及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健康政策用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从发达国家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地。不过,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世界其他各地的健康水平也应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了,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全球健康状况不平衡现象也应该消失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先进国家也在继续提升健康水平。在发达国家,婴儿与儿童的死亡已经变得极为罕见,而人均寿命的长度却仍然在持续增加。现在,健康问题的焦点已经转向了中年人和老年人。
人类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得以继续提升是本章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另外,本章也会探讨富裕国家人均寿命在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增加。这一章的内容也会让我们看到,在一个高度联结的世界,再继续以富裕与贫穷划分世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这对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交通和通信变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廉价,一个国家的健康创新几乎会瞬时影响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与普及可能用了100年,然而现代的医学发现却再也不会如此之慢。与此同时,如今疾病的传播速度也变得更加迅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寿命不平等的现象在逐步减少,但是寿命并非衡量健康水平的唯一重要指标,也不能因为寿命差距缩小就认定全球的健康不平等现象正在逐步改善。健康不平等问题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还不能就此进入历史的垃圾箱。健康,不仅仅在于人存在于世,还在于人如何存在于世。衡量“存在于世者”的健康状况,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身高。身高这一指标,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时期是否遭受了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的折磨有着非常灵敏的反应,它是对预期寿命这个健康指标的重要矫正和补充。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比过去的人长得高。不过也并非人人如此,在很多地方,人类在身高方面的进步非常缓慢。按照现在的速度,印度男性的身高需要再过200年才能达到今日英国男性的水平。这还不是最令人悲观的,因为印度的女性需要再过近500年才有可能赶上如今英国女性的身高。
对于富裕国家而言,从发现细菌致病理论开始的人类健康状况改善到1945年也未最终完成。在1945年,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就达到了今日印度的水平。到了“二战”之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就不再依靠婴儿与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了,与之相对的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成了寿命增长的主因。在今天的富裕国家,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肺结核、痢疾或呼吸道传染病,而是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1950年以后,富裕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速减缓,但仍保持增长。而推动他们预期寿命增长的,不再是干净的水或者更全面的疫苗接种,而是医学进步与人类行为的变化。
到1950年,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几乎已经完全消灭了传染病,到2000年,这项目标在发达国家全面实现。2013年,富裕国家约95%的新生儿预期寿命都要超过50岁。如此一来,人们要想再取得寿命增长,就得依靠中年和老年阶段的健康改善了。事实也是如此,在过去的50年里,中老年人的健康改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图4–1显示的是14个富裕国家的人口50岁时预期寿命情况。所谓50岁时预期寿命,就是指人们在50岁时预计自己还能再活的年数。如果50岁时预期寿命是25岁,就意味着这个50岁的人预计可以活到75岁。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样,这个指标也是假设人口死亡率会一直保持恒定。这张图显示的是男女的平均情况。实际上女性的预期寿命一般比男性长,但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不是性别之间的差异,而是整体的进步程度,所以就无须按性别来做出区分。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生不过70年,但是我们看图就会发现,早在1950年,图中所有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就都要大大超过70岁。即便是表现最差的日本,当时的人口预期寿命也超过了70岁。在1950年,各国之间的人口预期寿命差距相当大,比如挪威的人口预期寿命是27岁,芬兰的是22.8岁,日本的是22.6岁。在20世纪50~70年代的20年间,各国取得的进步不尽相同,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有国家的人口寿命增长都开始加速,而且出现了近乎同步的增长速度。这看起来像是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方式让国民变得更长寿了。在20世纪70~90年代的20年间,这些国家的人口50岁时预期寿命增加了近3岁。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的寿命增长仍然在继续,然而各国之间的差异又增大起来。比如,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极为突出,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丹麦则表现较差。
图4–1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1950年之后,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第二章中我们知道,在1950年之前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在那一时段,死亡率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婴儿与儿童阶段,成年阶段人口的预期寿命并未得到多少增加。这张图传递的第二个信息是各国表现不均衡,有的国家相对表现得更好一些。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在1950年时最差,但现在却是最好的。丹麦在最初位居前列,但如今却位居末席。美国曾经在中间时段有显著进步,然而如今却位列倒数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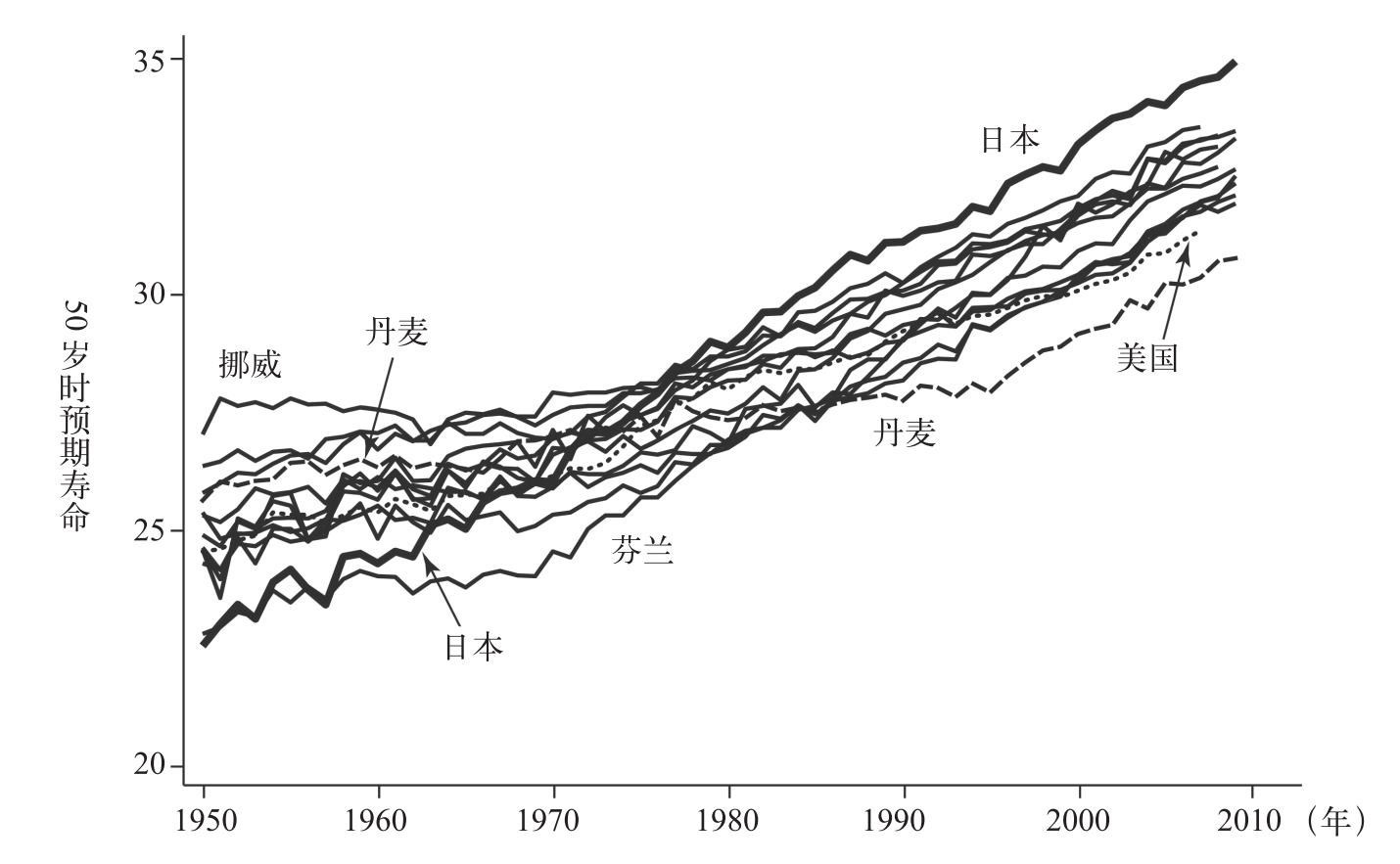
图4–1 富裕国家人口50岁时预期寿命(不分性别)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可能有非疾病与医疗方面的原因。没有人不想活得更久一些,人们都竭尽所能去逃避死亡,而政府机构也会竭力减少人口的死亡。对于一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而言,当大量孩子仍存在在成人之前就死去的风险时,想方设法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就成了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而在人们活到成年之后,未来的其他疾病就成了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些疾病会在人们老去时成为折磨,是另外一个致命杀手。既然儿童时期的危险已经不存在,那么,这之后的疾病风险就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个应当优先处理的选项。
在20世纪60~70年代,儿童死亡率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传染病也基本离人们远去。童年夭折风险消除之后,中年时期的人们又遭遇了新的致命风险:慢性疾病。慢性病主要包括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所谓慢性,是指这类疾病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是超过3个月。慢性也是相对急性而言的。急性病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有致命的危险,它们通常是一些传染性疾病。(把慢性病和急性病分别称作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或许更为合适。)
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种慢性病,尤其是同属于心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和中风的治疗上,我们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大量资金的投入。这不仅是指在治疗上的投入,也包括在研究上的投入。正是相关的研究,使得此类疾病的致病机理被发现,为制订更好的治疗方案创造了条件。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也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而类似于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疾病则会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在1950年,我们不可能过多考虑老年痴呆这样的疾病,在1850年更是如此。毕竟在当时,多数的人们都还活不到能得老年痴呆症的年纪。在19世纪,新的疾病催生了新的治疗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发现新治疗方法的机会。今天也同样如此,当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那些折磨老年人的疾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要理解当今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死亡原因,吸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在20世纪的上半期,吸烟人口出现了全球性扩张,而在之后,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又同时出现了吸烟人口下降的情况。最初,女性吸烟的情况要比男性吸烟的情况少见很多,并且,女性开始吸烟的时间一般都比男性晚,而在吸烟人口出现下降的国家,女性戒烟的时间也比男性要晚。吸烟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直接的愉悦,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吸烟都是一种廉价且具有交际性的消遣。对于很多穷苦人民来说,烟草易于获得,而且也能支付得起,他们可以通过吸烟获得一种从繁重的工作中逃离的快感。但是吸烟也会引发疾病,导致死亡。肺癌和吸烟密切相关,尽管不是所有的吸烟者都会罹患肺癌,但几乎所有的肺癌患者都曾吸烟。由肺癌导致的死亡,一般要晚于吸烟本身3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即便吸烟行为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死于吸烟的情况仍然会出现。吸烟还有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而且在这方面导致的死亡人数比肺癌所导致的还要多。此外,吸烟还会导致呼吸道感染等类型的疾病,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这种病会造成呼吸困难,是引发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卫生部于1964年发布的《吸烟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报告》(以下简称《影响报告》)被视为是引发人们改变吸烟行为的关键一环。很多美国老年人承认他们在报告发布之后就戒掉了烟瘾,或者至少开始下决心戒烟。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卢瑟·特里博士自己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起初,为了降低公众的关注度,这份《影响报告》的发布会定在了华盛顿周六的一个早晨举行。特里博士在前往发布会现场时还在车里抽烟。他的一个助理提醒他,发布会上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问部长本人是否抽烟。特里非常恼火,因为他认为“这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到了现场,果然第一个问题就是抛给特里的。特里犹豫了一下,接着宣布道:“我戒烟了。”接下来人们又追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戒的?”特里回答说:“20分钟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众多的美国民众效仿卫生部长,纷纷开始戒烟。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香烟销量达到了顶峰,按人均计算,当时大约每个成年人每天要吸掉11支烟。而实际情况是,当时有40%的美国人吸烟,即平均每个人一天要抽掉1包多的烟。
不过,说卫生部长的报告改变了一切也并不准确。在这份报告之前,就有很多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问世了。我妈妈在1945年的时候怀了我,当时医生就要求她戒烟。如果没有这个建议,有可能现在不会有我在这里写这本书。在美国,1964年烟草销量达到顶峰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1964年以前,美国就开始出现男性吸烟人数下滑的趋势,而女性吸烟人数在1964年之后还持续上升了一段时间。因此,1964年出现的见顶状况只不过是这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今,至少在富裕国家中,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知。有人可能因此而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都在减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且在男女性之间,吸烟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国家不同,烟草销售带来的收入和相应成本也不相同,这就使得各个国家在如何提示吸烟风险以及公共场所是否应该禁烟等问题上有不一样的态度。不过,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男女之间在吸烟上的差异。在部分国家,女性吸烟是一种遭到排斥的行为。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如果一个女人当街抽烟,就有可能被我妈妈这样的人当成妓女。如此一来,吸烟权就变成了女性追求权利平等的一项内容。在美国、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女性的吸烟比例很快就追上并超过了男性。当然,如今无论男女的吸烟比例都有所下降。日本男性的吸烟比例一度非常高(在20世纪50年代时接近80%),不过现在也出现了下降;相比而言,日本的女性倒是很少吸烟。在欧洲大陆,吸烟人口的比例也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是也有不少例外,尤其是女性的吸烟比例并未出现这种趋势。有一个幽默的说法,之所以其他国家的吸烟问题仍然严重,是因为卫生部长的那份报告没有被翻译给其他国家的人看。
吸烟的普及几乎和细菌致病理论的普及一样,也不过是近100年的事情。吸烟仍是或者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也是或者曾经是人们愉悦的源泉。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后,吸烟的人就开始减少了,但是人们总会有补偿心态,更不用说吸烟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戒掉的习惯。杀菌去病,意味着要认真做好日常家务,保持好卫生,但同时也意味着要纠正一些此前的顽固乃至代价高昂的习惯。在这些过程中,性别非常关键。女性通常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要做好这些工作,杀菌消毒的工作就不可少,在很多家庭中,女性因此有了“杀菌警察”的称号。而在吸烟这件事情上,女性最开始扮演的是被压迫者的角色,但后来就成了被解放者。我们需要记住,尽管现在的烟草已经被妖魔化,吸烟也常常被当作一种流行的瘟疫或者疾病,但吸烟的危害程度毕竟和霍乱或者天花不一样。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吸烟也的确有些诸如黑死病或者乳腺癌之类疾病所不能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认为吸烟所带来的愉悦,大于对其健康所造成的损害,那么吸烟也未必是一个不理性的举动。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政府从吸烟的人身上赚到了不少钱,这些人多数是穷人,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抵消富人赚的物业税。抽穷人的税,使富人得利,这样的税收政策看不出有任何符合公共健康利益之处。
图4–2显示,吸烟和因肺癌死亡人数这一指标有正相关联系。这张图显示的是自1950年以来,几个主要国家50~69岁人口死于肺癌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以及西北欧国家,美国在图中用粗线加以突出。在左侧表示男性吸烟与肺癌关系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左右,也就是吸烟人口达到高峰的20~30年后,因肺癌死亡人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右侧女性吸烟与肺癌关系的图则显示,因为女性开始吸烟的时间比男性晚很多,因此在1990年之后,因肺癌死亡人口只是在其中的几个国家出现了下滑。右侧的这一图形,看起来就像一只鳄鱼张开的下颚。虽然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女性因肺癌死亡的比例也在下降,但总体上肺癌发病的高峰期仍在持续。女性吸烟量从来都低于男性,同时早期吸烟的女性比例也相对较低,因此她们的死亡率也比男性的要低,即便是那些吸烟女性死亡率较高的国家也是如此。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肺癌是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占美国总人口40%的吸烟人口中,因肺癌而死(或将死)的人却只占一小部分。在美国,最高的平均年肺癌死亡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200人死亡,即0.2%的死亡率。
虽然同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罹患肺癌的概率要高10倍甚至20倍,大多数吸烟者还是不会患上肺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一个计算罹患肺癌风险的在线计算器。比如,一个50岁的人,每天抽1包烟,连续抽了30年,那么,如果他从现在开始戒烟,就有1%的肺癌发病率;如果他继续这样抽烟,则他罹患肺癌的概率就要达到2%。不过,吸烟者也不要因为这个结论就觉得欣慰,因为患上肺癌并不是吸烟者唯一的风险,也不是最严重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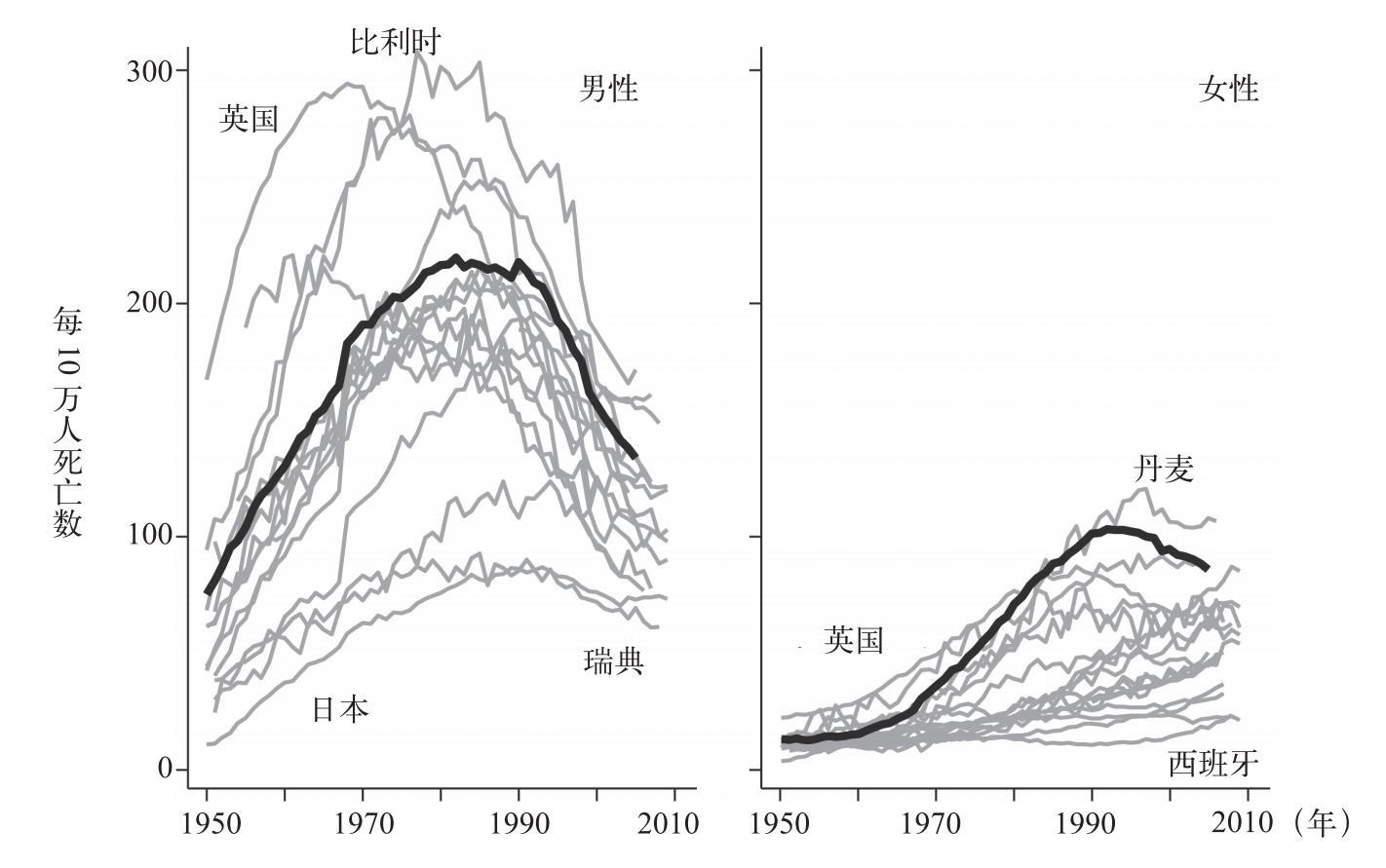
图4–2 肺癌死亡率(粗线表示美国)
吸烟导致了近年来的女性预期寿命增速低于男性。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很多女性吸烟现象出现较早的国家,比如英国、丹麦以及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烟草公司将吸烟与女性解放成功地联系在了一起,可是最终美国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在美国,吸烟的广泛盛行是造成美国人50岁时预期寿命增速低于日本或法国等富裕国家的最重要原因。近期的相关统计估测,假如不吸烟,美国人的50岁时预期寿命将比现在的长2.5年。
与肺癌死亡率下降相比,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显著。心血管疾病包括中风、动脉硬化(血小板聚集导致动脉堵塞)、冠心病、心力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心绞痛等病症。男性减少或停止吸烟降低了患上这类疾病的风险,但治疗手段的突破也对防治心血管疾病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医学界尚未在肺癌的防治手段上取得类似的突破。
图4–3显示了1950年以来中老年人(55~65岁)在心血管疾病上的死亡率。左边的部分显示的是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右边则包含了图4–2中提及的所有富裕国家。从图上可以看到,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是极高的,它几乎是肺癌死亡率的5倍。在20世纪50年代,有1%~1.5%的中老年人可能因这类疾病而死。从那个时候至今,心血管疾病一直是高收入国家人口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要高于英国;不过,在美国,由这种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正在慢慢下降,而在英国,这种死亡率却在慢慢上升。右图显示,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冰岛和荷兰的死亡率则处在最低位置,至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死亡率,则一直处在高高低低的交错变化之中。到1970年,每个国家的变化趋势都变得较为明显,各国之间相互交错的情况逐渐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很多,吸烟自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具体到各国,则致病原因并不相同。
1970年之后,各个国家的情况变得大不相同。从这时起,美国等国家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开始下降。当然,每个国家具体的下降时间点略有早晚之分,比如英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在七八年之后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全世界的死亡率在同步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芬兰也不例外。从图中可以看到,芬兰在1970年时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还高达1.5%,但是此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到21世纪初,已经降低了一半。此外,在21世纪初,各国的相关疾病死亡率都变得十分接近,20世纪50年代那种国与国之间的明显差距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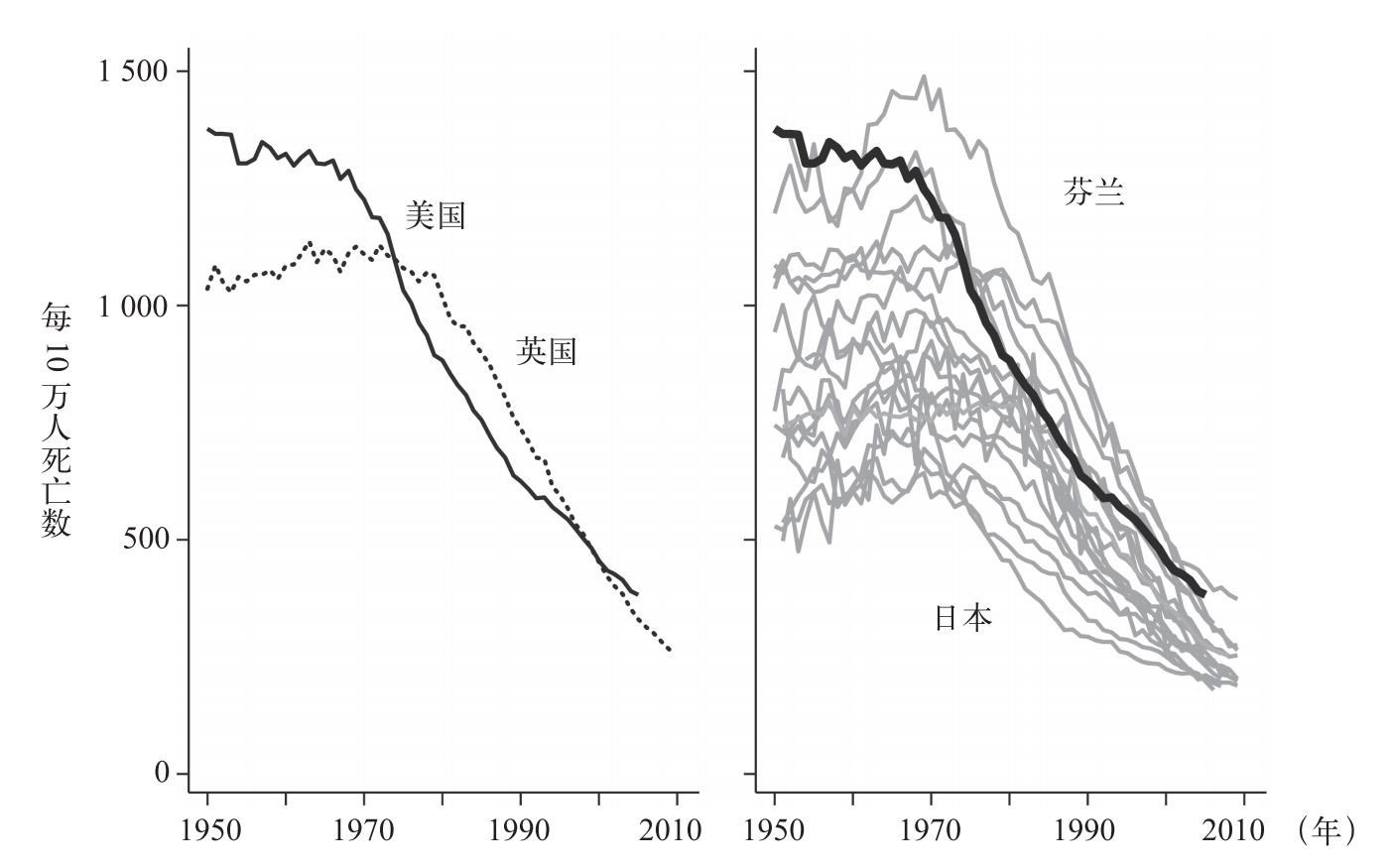
图4–3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右图中的粗线代表美国)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抽烟减少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过,由于各国之间的吸烟状况差别很大,而且抽烟这种行为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出现迅疾改变,所以抽烟减少这个解释也并不一定合理。另外,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健康权力机构可以强制这么多国家同步发生改变,即便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即认为是医学进步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成本低廉但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而达到防治同一种疾病的目的。
在心血管疾病这一领域,“卡托普利”的应用算是此种类型的一项关键创新。卡托普利因为会导致尿频而有时被称作“利尿剂”。这是一种价格低廉但非常有效的降血压药,而高血压则是导致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梅奥医学中心称:“卡托普利……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对盐(钠)和水的代谢。它可以让你的肾将更多的钠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相应地,钠会把血液中的水带走,这样,血管中的液体量就会减少,其对动脉壁产生的压力也就相应地降低了。”1970年,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降压药对高血压的重要作用,此后,降压药疗法在美国迅速普及。
美国医疗系统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新的发明总会很快被付诸应用。这不但包括像普及降压药这样的有益之举,有时甚至一些作用不甚了了的创新也会被迅速推广开来。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则因为是中央统一管理,资金被约束,所以在新的医疗手段引进上要相对缓慢和谨慎。这就意味着像卡托普利这样物美价廉的药品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测试之后才能应用。不过,英国如今建立了一家名为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的机构,专门从事新药与新治疗方法的测试和推荐工作。图4–3右面部分显示出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和英国的类似:尽管各国地方机构和医疗系统千差万别,但在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之后,各国也逐步出现了死亡率下滑趋势。
卡托普利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降压药物,此后,诸如ACE抑制剂、钙通道阻滞剂、β–阻断剂、血管紧张素拮抗剂之类的多种降压药物相继出现。如今,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为其选择最合适的降压药物。另有降压药物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降胆固醇类药物同样有助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药物的使用都属于预防措施,旨在降低人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而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面,其实也有不少新的方法。比如,当一个人因心脏病突发被送至医院时,医生应第一时间给病人服用阿司匹林。这是一种十分有效同时成本低廉的救治手段。还有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医疗手段,比如心脏搭桥等,也是救治心脏病患者的重要方法,并降低了他们的死亡率。不过,这一类的医疗救治确实花费不菲。一项临床试验显示,中年人每天服用婴儿剂量的阿司匹林,总体上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但是,后续研究也证实,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让一些人摆脱心血管疾病,但确实也引发了一小部分人的死亡。整体和个体之间常常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在一片阿司匹林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尽管如此,医疗手段和预防手段的创新还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降低了这项高致死率疾病的风险。在过去,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些人本来或许早已被心血管疾病夺走了生命,但如今却可以安心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事业与感情生活,更有了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
同肺癌的情形类似,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也要比男性低很多,大概只有男性的一半。同男性一样,各国女性的死亡率也在下降,下降幅度在50%左右。此外,各国的死亡率下降趋势也表现出类似程度的协同性。这样一来,如今各国的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相差无几,国与国之间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那样大的差异与变化。一句话,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起初就比男性低,如今风险总体下降,则女性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就更低了。同男性的情况一样,心血管疾病也是导致女性死亡的最主要疾病。尽管人们经常认为乳腺癌是女性的重大潜在杀手,但实际上,死于乳腺癌的女性比死于心脏病的女性要少得多。
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之间,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没有拉开差距,反而趋向一致,这一点是极为罕见的。同半个世纪前相比,各个国家的心脏病死亡率更加接近。100年前出现的细菌致病理论,曾经拉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健康水平差距,但这种情况却没有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上重演。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现在的这些重大医疗进步成本低廉,可以被轻易复制仿效,因此各个国家可以迅速将其推广运用。不过,从每个国家的内部看,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因为医疗成本的低廉而消失。实际上,心血管疾病防治上的进步,可能已经扩大了一国内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教育背景更好、经济状况更好,或者本身健康状况更好的群体,会在接受个人治疗方面大大领先其他群体,比如他们会更早地进行定期体检,更早地关注血压和胆固醇指标。
癌症是紧排在心脏病之后的第二大健康杀手。除了肺癌之外,最具威胁的癌症是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其中乳腺癌患者几乎都为女性,前列腺癌患者皆为男性,而结直肠癌则威胁着男女性的共同健康。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在癌症的治疗方面依然没什么建树,癌症的死亡率也没有出现下降。美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对癌症宣战,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以至于那些近乎最权威的评论也认为,人类对癌症的这场战役已然失败,或者说至少没有获得成功。在这本书中,我始终强调,需求导致了新知识的发现和新的医疗手段的出现,但是需求不见得总会创造供给,几十亿美元也好,对某种疾病宣战也好,都不会必然导致某种疾病被攻克。我们在癌症治疗上的失败就是明证。
不过进步还是有的。有证据表明,这三种癌症导致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可能已有时日,但与此相矛盾的是,这一成就可能被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遮蔽了。我们在迷宫游戏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成功地摆脱第一个怪物后,却常常命丧它后面那个怪物的手中,即便这个怪物可能没有之前的那个那么有杀伤力,但还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与此类似的逻辑是,当一个人摆脱了心脏病之后,可能就暴露于某种癌症的危险中,而如果一系列风险因素(比如肥胖症)叠加,这种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降低就意味着因癌症而死亡的风险增加了。以往我们认为,只有以上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真实出现时,才能说在攻克癌症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近来癌症死亡率的下降事实却直接证明,在与癌症的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乳房X光摄影检查、PSA测试、结肠镜检查等经常被认为是降低各类癌症死亡率的功臣,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它们的作用,尤其是乳房X光摄影检查和PSA测试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比如,有了乳房X光摄影检查之后,早期诊断的数量大幅增加,按说晚期诊断会因此出现下降,但这样的情况却并未发生。在过去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女性被筛查出患了乳腺癌,但实际上这些人却从未发病。医学治疗水平的提升也是乳腺癌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比如通过服用他莫昔芬来治疗乳腺癌。肿瘤医师兼历史学家悉达多·穆克吉在其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 [1] 中指出,经过几代医学与化学治疗的反复试验之后,我们对每一种癌症的起源渐渐有了更好的科学理解,并开始逐步使用起更为新颖有效的治疗方法。
很多针对心血管疾病的新治疗手段非常有效,也都很便宜,但是癌症的新疗法则常常非常昂贵。而治疗价格的昂贵也会制约治疗手段本身在国家与国家间的传播。筛查本身并不贵,但却可能导致大量后续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比如说,通过筛查,没发现患病,但发现有致病因素存在,比如高血压、高胆固醇,甚至是疾病遗传倾向。这样就需要接受各种治疗,比如吃降压药、吃降低胆固醇药;极端的情况,因为有患乳腺癌风险,还要切除乳房。这些做法当然会拯救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高血压之类的问题根本不会发展成某些大病。而即便是筛查手法十分有效,它也会带来某些不公平:受教育程度高的或者对这种医疗知识了解的人,总会比其他人更早地运用这种技术来发现疾病。不过,在未来,筛查肯定会变得更加有用,不必要的筛查将会得到控制,药物和治疗手段则会因为更广泛的应用而变得更为便宜。如此一来,癌症也就可能和心血管疾病一样,可以成功地被科学和医学所征服,人们也因此可以更长寿、生活得更好。
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在对死亡率产生影响,尽管它们作用并不明确或者仍充满争议,其中之一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数量更丰富质量更佳的食物。在19世纪食不果腹还是一种常态的时候,说营养改善可以降低死亡率,是貌似有道理的一件事。但如今,我们担心的已经不再是人们吃得太少,而是吃得太多。不过,若将现在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部分归功于70年前他们在母体、襁褓以及儿童时期的营养改善,也不无道理。20世纪70年代,芬兰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最高,这可能与“一战”时期它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有关,那时出生的人,到20世纪70年代时正处在55岁左右。
人口学家伽比利·多波汉摩和詹姆斯·沃佩尔发现了食物对寿命产生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他们统计得出,在北半球,10月出生的人50岁时预期寿命要比4月出生的人高半年。在南半球,除了那些出生在北半球然后搬过来的人之外,其他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对这一发现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即便是在富裕国家,绿叶菜、鸡肉、蛋等也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会价格便宜供应稳定;而这意味着还在母亲肚子里等待着秋天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不过,随着食物供应的季节性差异日益缩小,这种效应已经随着时代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小。
死亡率下降值得欢欣鼓舞,因为我们都想更长寿。但是,这并非健康水平提高的全部内涵所在。我们也想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健康,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盯着死亡率而忽视了发病率。有身体或者精神不健全问题的人,或是有慢性病或者抑郁症的患者,都会在让生命更加精彩这方面有所欠缺。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经过反复试验的一项进步就是关节置换术,尤其是髋关节的置换,现如今已经是一项例行手术。髋关节出问题的人可能要承受终生的疼痛或者一辈子不能动弹,而置换手术的神奇效果,使得原本可能充满困苦、病痛以及受限的人生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同样,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可以令病人的视力恢复,甚至比之前更好。这些医疗手段,都使原本要失去某些能力的人,重新焕发活力。止痛药比以前的更有效,1984年布洛芬出现,它可以缓解多种情况下的疼痛,起到阿司匹林不能达到的效果。健康专家对此的认知也不断加深,他们给病人更大的自由去掌控止痛药的用法用量。抗抑郁症药物让很多人的生活得以改善。人们可以比以前更方便接触到专业医学人士——这非常重要,尽管有时候医学人士也无能为力,但他们至少可以让重视自身或亲人健康的人们觉得安心。退一步讲,即便他们也不能让人安心,但还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造成神经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求医问药都需要费用。这些费用要么是个人负担,要么是保险公司负担,要么是国家负担。美国人在健康保障上花的钱出奇的高,他们将国民收入的18%花在了这上面。不过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于那些极富疗效却通常价格昂贵的新医疗手段,美国人也感受到费用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节省医疗开支,很多国家在医疗获取上增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公费医疗系统就严厉限制肾透析的人群规模,它规定,只有足够年轻的人才能得到透析机会,50岁以上的人被排除在外。理由是,50岁以上的人都差不多是“易碎品”了,给他们做肾透析就是浪费金钱。曾有一段时间,英国人做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种医疗服务不足的情况,导致了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双双上升。现在,在英国做肾透析和关节置换手术没有以前那么严格的限制了,但英国还是希望能够控制这种新药物和新治疗手段的引入。我前面提到过的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就是一个测试新药并发布效用报告以及评估这种新药物是否物有所值的机构。但这个机构遭到了制药公司和医药设备生产商的强力抵制。因为早期得到过这家机构的不利评价,至少有一家制药公司曾威胁要撤出英国,不过,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坚持立场,没有妥协。
医疗保健品的供给多少就是过量、多少算是必需,经济学家和医生群体对此存在分歧。有人强调医学的重大功用,他们称,如果对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合理取值,就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而绝对不是更少,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多花一倍的钱就能得到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比例的下降,那么就应该这么去做。这类计算当然存在错误,因为它们把死亡率的下降全部归功于医疗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比如吸烟的减少对死亡率下降就有很大影响。不过,这种应该花更多钱在医疗上的观点也有合理之处。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随着富有程度的提升,没有比把钱花在延年益寿上更好的事情。比如美国的医疗费用比欧洲的高,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服务比欧洲的更为奢华:美国有比欧洲更多的单间或者半单间医院病房,美国人在诊断和检查上花的排队时间更短。这当然很好理解,毕竟美国人整体上比欧洲人富有,足以支付这些费用。
另一派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承认医疗保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福音,但认为更应该关注现有医疗体系中存在的浪费现象,以及类似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较为缺乏的现状。现有医疗体系中的浪费现象造成了医疗支出水平的提升,而像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类机构的缺乏,使得很多医疗手段在其有效性未经验证的情况下就被应用,从而又导致了医疗开支的加速增长。记录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开支情况的“达特茅斯医疗卫生地图”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它用一张地图展示了美国不同地区间医疗保健支出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与医疗需求和医疗效果都无关。实际上,根据地图,医疗支出和医疗效果是呈负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不少医院和医生在检查和治疗的推行方面太过激进,而由此增加的支出效果却不甚明显,甚至没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甚至对病人造成了伤害。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的确可以大幅缩减,而健康水平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高质量的医疗可保障并促进人类的健康,是实现幸福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因为医疗保健服务价格高昂,因此,高额的医疗开支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开支之间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美国人在医疗上的开支增加1倍,那么他们就必须把在其他方面的开支都减少1/4。如果我们遵循达特茅斯医疗卫生地图的建议,把医疗开支降低一定的数额,比如降低一半,那么,我们在其他各方面的开支就可以增长近乎10%。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权衡取舍处处可见,只不过,诸如多买了几本书或者几件电子产品因此无钱度假这种事情,一般也并不值得担忧,那么为什么到了医疗问题上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与可以在买书支出或度假支出上做出自由选择不同,人们在医疗上的开支无法自我选择。实际上,人们可能并不清楚他们为医疗保健支付了什么,或者他们在得到医疗服务的同时,放弃了什么。在美国,多数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由政府通过老年人医疗保险来支付的,而多数(59%)非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则由雇主提供。很多人认为,是雇主为他们支付了医疗保障所需的钱,自己分文未掏。但是,大量研究早已证明,最终支付这些费用的并不是老板,而是雇员自己。老板们并没有因为支付这些费用而降低了利润,他们只是降低了雇员的工资。因此,如果不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上涨如此之快,人们的平均收入以及主要基于此的家庭收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涨得这么慢。不过,普通人却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医疗费用的上涨是收入增长缓慢的罪魁祸首,不知道医疗成本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在欧洲等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或者是有老年人医疗保险的美国,同样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当人们要求政府提供额外的医疗福利时(比如要求政府报销处方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会为此放弃什么。美国最著名的健康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一位老年女性若想动手术,则不管费用多么昂贵,老年人医疗保险都会为其全额支付,哪怕这个手术不是很紧要,也并不一定有效。但这位老人的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连买一张机票去参加女儿婚礼或者看孙子的钱都没有。这种类型的权衡交易,一般都要经过民主辩论等相关政治程序来达成,但是这个政治程序本身就充满各种问题和争议,并且很难保证人们的知情权。在一些国家,这个程序还可能受到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严重干预,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利益:医疗开支越多,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就越多。
收入和健康状况是决定人们能否幸福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本书的讨论重点。我们不能将它们分开考量,也不能仅让医生病人去游说政府要求更好的健康保障,或仅让经济学家鼓吹经济增长,因为这两者不能顾此失彼。今天,医疗服务一方面非常有效,另一方面也非常昂贵,这就需要做出权衡。用福克斯的话说,我们必须要用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的幸福问题。要允许我们能持有这样的视角,相关程序就需要落实到位,诸如英国的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医疗费用的无限增长对人类幸福其他层面的威胁,也需要得到公众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认知。
未来将会怎样?高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还会继续增长吗?人口和社会学家杰伊·奥利尚斯基对此就持否定观点,他认为,增加人口预期寿命将变得越来越难。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有所感知。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对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巨大影响,因为儿童的生存时间还有很长。但是当儿童的死亡率几乎为零时,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却不能对预期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章图2–1就显示出,在1950年之后,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可以预见,这样的增长下滑在未来还会持续,因为即便科技创新会持续,未来医学的重心也会放在老年人身上;而即便是癌症被攻克,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不过只是增加四五岁。悲观主义者还发现,在多数发达国家,肥胖症患者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未来人口死亡率的上升。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目前还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证据,毕竟随着心血管疾病治疗方式的改进以及抗胆固醇和降压药物的应用,肥胖症的风险已经没有最初研究的时候那么高。
另一方面,人口学者吉姆·厄彭和詹姆斯·沃佩尔在2002年公布了一张重要的图,对1840年以来全球女性每年的最高预期寿命进行了统计,而由于女性预期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这些数值可以看作每年人类最高的预期寿命值。根据该图,在过去的160年中,这些数值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并且平均每过4年,世界的最高预期寿命就会增加1岁。因此这两位学者说,没有迹象表明,在未来这一长期的趋势不会继续保持。他们的这张图还收集了大量之前关于人类最高预期寿命的预测数值,结果发现,这些数值都已经被实际的数据所超越。之前有很多学者预测人类的寿命增长将减缓或者停滞,但是他们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支持人口预期寿命可以继续增长的乐观观点则认为,现在的人们都想要比自己的预期寿命活得更长。当物质上变得更为富有,人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避免过早死亡,而他们也会将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在延年益寿上。过去的人们便是如此,因此也没有理由怀疑,在未来人们不会继续这么做。
我个人认为乐观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学会了打破权威,并开始运用理性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让生命变得更好的道路,因此无须怀疑在未来人类还会继续战胜死亡。不过即便如此,认为人类预期寿命还会以和之前一样的速率增长,也未免过于乐观。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带来了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但是这方面的条件至少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耗尽。在过去的160年中,人类预期寿命之所以可以每4年增长1岁,主要原因就是儿童死亡率一直在下降,但这一点在未来却不会持续。当然,这里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将预期寿命长短作为衡量是否幸福的唯一指标。如果癌症和其他的老年疾病能被消灭,人类的痛苦将大大消减,亿万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提高。如果我们以这些改善不能有效提升人类预期寿命为由而轻视其重要性,显然是没有抓到重点。
在这一章和第三章我们分别讨论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健康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要将这两个群体合二为一进行讨论,并考察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过去的50年,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全球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全球化当然不是史上第一次,但是它的确是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今天,交通变得更为便捷且成本大幅降低,信息流动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全球化对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改变了疾病的传播速度以及健康信息的流动速度和医疗手段的推广速度。不仅如此,全球化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双边贸易的增加,都间接促进了人类健康的改进。
历史上存在多个全球化的周期。有的时候,全球化是通过战争、征服以及帝国的扩张等手段实现的;有的时候全球化的实现则是得益于新贸易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商品和财富。疾病经常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而来,其结果是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说,原先,西方、南亚和东亚存在的疾病各不相同,“仿佛它们不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但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贸易的发展却把这些疾病带到了世界各处,于是在中国和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会同时出现灾难性的疫情。1492年以后的“哥伦布大交换”是一个更为人熟知的例子。很多历史性的疾病大流行都是从贸易新航路的发现或者新的领土征服开始的。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就是由贸易所引发,黑死病则是在1347年由商船上的老鼠带入欧洲大陆。19世纪欧洲的霍乱大流行,通常被认为是拜来往印度的英国人所赐,而其后来在欧洲和北美的加速传播,则是因为铁路的出现。受病毒感染者经常是在自己未知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城市穿梭,这样,霍乱病毒就会沿着铁路线一直传播。而现在,过去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间,如今可以从这个半球飞到另外一个半球了。
全球化促进了疾病的传播,但也为医疗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之前谈到的细菌致病理论就是一个例子。细菌致病理论在19世纪末的北美被发现以后,到1945年之后就被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1970年之后,依靠药物控制血压的知识也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导致相关死亡率在全球同步下降(见图4–3)。吸烟引发癌症的新知也以同样的方式迅速传播。在人们还未搞清艾滋病的起源之时,这种疾病就已经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的相关医疗对策研究,从病毒的发现,到传播途径的推演,再到相关的化疗方法,都发展得十分迅速,尽管仍然有成千上万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但以先前的标准看,这次对艾滋病的应对已经极为迅捷了。如今虽然人们对艾滋病的理解仍不完善,但科学应对艾滋病的方式仍得以强化,不仅是富裕国家,就是那些疫情最为严重的非洲国家,这两年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已经出现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开始逐步回升。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防控手段也在快速传播,不仅仅在富裕国家传播,也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因为由传染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下降,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就变得更为重要。除了非洲,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最主要的致死病因。像降压药这样便宜而有效的疾病预防药物,应当和以前的疫苗接种一样大力推广,不过,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一个以医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进行组织和监管,可能是实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一些更为昂贵的医疗手段,比如某些癌症的治疗和关节置换手术等,也得以在穷国应用,但是这样的医疗服务一般只服务于穷国中的一小部分权贵与富裕阶层。
在健康方面,富国对穷国的影响并非总是良性的。不同于经济学家,健康研究者常常视全球化为一种负面力量。吸烟问题是研究者深度关注的一个方面。在富裕国家,烟草产品已经不再受到追捧,但是烟草公司发现,穷国是他们销售烟草产品的天堂,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是在烟草方面监管无能,要么就是毫无监管的利益动机。医药的专利制度使得药物价格高昂,因此也受到了大量质疑,但是专利制度是否真是问题所在却仍存争议。这里还涉及一个政府缺乏药品引进能力的问题,毕竟世界卫生组织清单上所列举的核心药品基本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当然话说回来,要是药价能够更便宜的话,这个核心药品名单上的产品肯定会更多。在与强大富裕的国家进行多边贸易谈判时,弱小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发现自己身处劣势,因为前者无论是律师团还是游说团的规模都要比他们的大很多,而那些医药方面的游说者,根本就不会关心穷国的健康问题。第一世界的医学进步显然加剧了穷国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在德里、约翰内斯堡、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这些地方,权贵与富裕阶层可以用上第一世界国家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和设施,然而在这些地方,却到处可见那些医疗条件连17世纪欧洲人都比不上的穷人。
1950年以后,世界的健康状况和健康不平等状况有了哪些变化?通过第三章的图3–1,我们已经发现,人均预期寿命的地区差距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收缩,原先预期寿命最低的地区已经接近那些原本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现在我们再以国别为单位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图4–4显示的是典型国家的预期寿命变化。它显示了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与最好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显示了这种寿命差距的变化情况。整张图看起来像是一架管风琴,但实际上这是一组箱形图。图中,纵轴表示预期寿命,中间的箱形表示各国预期寿命的集中区域。这张图传递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自左向右(从1950~1954年到2005~2009年)这些箱体的位置在不断抬高,表明全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在逐步增长。每一个箱形图的箱体区域都包括了世界上一半的国家,箱体的中线则表示预期寿命为中位数的国家。从图中可见,这些中线的位置一直在抬高,虽然近年来的抬高速度相比50年前明显要慢了不少,但还是表明这些预期寿命处在中位数的国家,其平均寿命值在不断增长。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人类预期寿命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快后慢的增长趋势,主要在于以前我们是大幅降低了儿童的死亡率,而现在则更多的是在关注老年人的健康情况。每个箱形上下有横杠的线须,表示另外一半国家的预期寿命,加上箱形区域,这张图就把所有国家的寿命情况都展示了出来。当然,一些极端的国家是被排除在外的。在本图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极端位置,它们是卢旺达和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在1990~1995年间都处于内战状态。我们统计了192个国家在每个时间段的预期寿命情况,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有的是由主观估算得来,尤其是早期的那些。
这张图还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图中的箱体部分变得越来越小,这表示所有国家的预期寿命数值都在向中位数靠近。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在缩小,以此观之,说明在健康方面全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在减少,始自250年前的健康不平等现实正在被改写。不过,这种差异缩小趋势并非总是出现,比如在1995~2000年,由于非洲艾滋病的蔓延,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再次出现了扩大现象。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差距缩小的趋势才得以恢复。每个箱体中横线的位置也在不断抬高,越发靠近整个箱体的上部以及线须的最高点,这种情况说明,预期寿命处在中位数的国家与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变小了。现在,中位数与最高值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10.5岁(中位数为72.2,最高值来自日本,为82.7)。不过,中位数与最高值的差距缩小也意味着中位数与最低值之间的差距渐渐扩大。即便不考虑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特殊情况,从最低值到中位数的距离,也从最初的22岁,增加到了如今的26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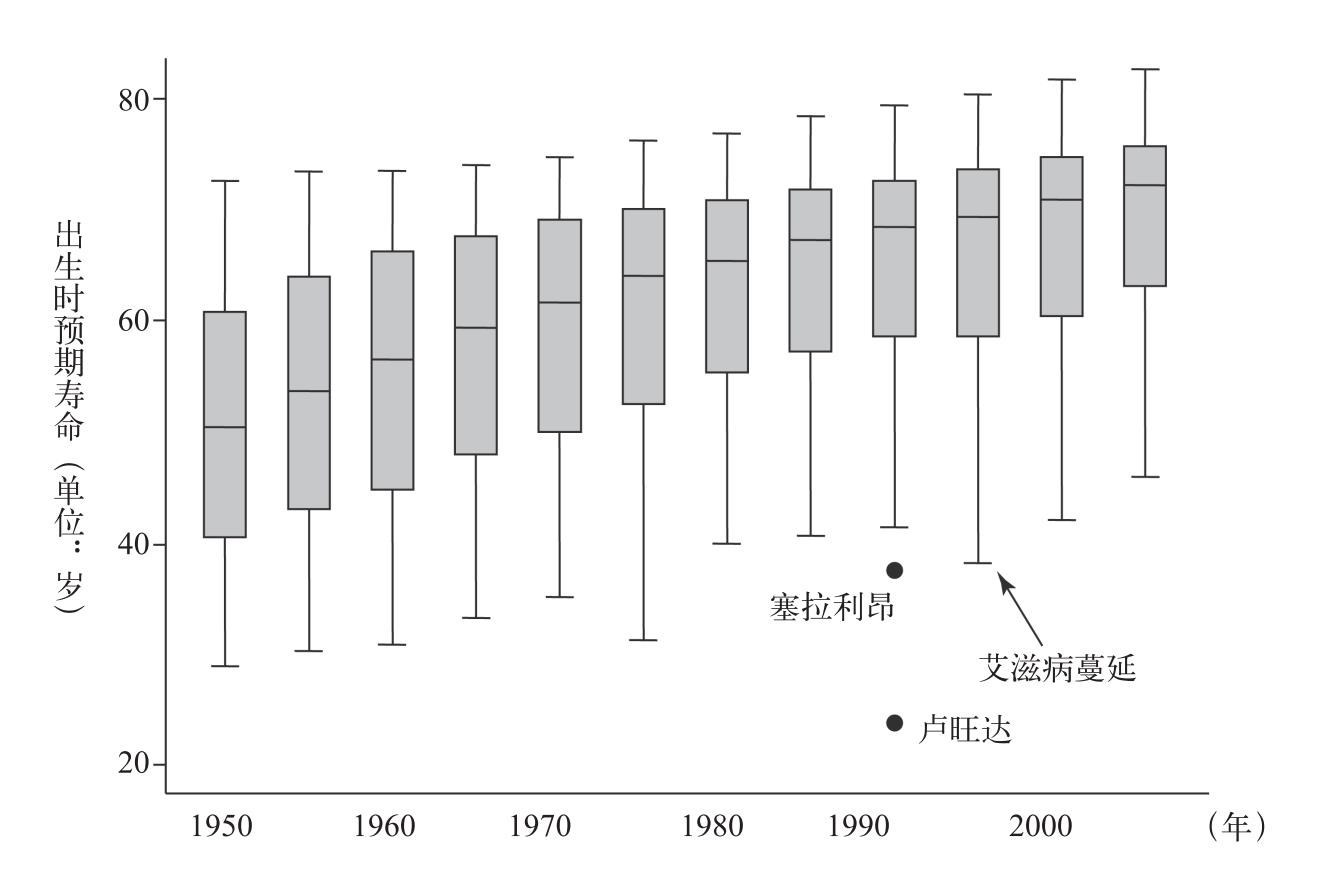
图4–4 预期寿命及其世界分布
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思考,预期寿命是否是考察健康不平等问题的一个好指标?通过本章我们已经知道,预期寿命的增长,主要源自贫穷国家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富裕国家中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当我们使用这种指标来比较穷国和富国的时候,实际上是给了穷国一个更高的权重,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比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对预期寿命这个指标的影响更大。而这才是穷国和富国之间预期寿命差异缩小的最主要原因。以预期寿命长短作为衡量平等与否的指标,实际上已经是在认定降低儿童的死亡率要比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更为重要,但这样是否合理却值得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孩子在未来会怎样,至少他也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时间;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延长老年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虽然老年人已经没有多少余命,但是他们比刚出生的孩子更与这个世界休戚相关。总之,我们很难确定地说以预期寿命来考察健康的不平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实际上,如果对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重视程度,我们便可能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全球不同国家在预期寿命上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变得更好了,因为预期寿命不能反映我们所关注的健康的全貌,甚至不能反映生死问题的全貌。的确,我们现在的世界,穷国的儿童死亡率在下降,富国的成年人寿命在延长,但是否就可以以此来说明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对各类人群的死亡率重视程度不同,那么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讨论一直没有结束。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之后,人们生育的意愿也随之下降。1950年,非洲的每个女性平均要生6.6个孩子,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5.1。而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4.4。在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每个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字更是从6下降到了2点多。在死亡率下降之后,生育率并没有随之下降,所以人口大爆炸的现象才会出现。但是最终,当父母们发现再也不会有这么多孩子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减少生育的数量。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生育同以前一样多的孩子甚至更多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也会安然长大成人。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原本可能生下来就会死去的孩子,现在根本就没有被生出来。那谁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看待不同人的生命权重,而这是一个让哲学家都无法判断的问题。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那就是妈妈们从中受益不少。现在,她们不用像以前那样经常地怀孕,同时她们和丈夫也不用再承受子女早夭的痛苦。此外,对于女性来说,生育负担的减轻不仅仅减少了痛苦的来源,也使得她们有更多时间关注生活的其他方面。她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走出家门工作,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更为多样的角色。
在人类健康方面,1950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确可喜可贺。人们逐渐远离死亡的威胁,世界各地之间的寿命差距也逐渐缩短。但是,在营养的均衡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却难说突出,世界各地的营养水平更是存在巨大差别。考察营养失衡的问题,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看一下人类在身高上的变化。
身材高低本身并非衡量幸福的标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一个身高180厘米的人就比一个160厘米的人要富有、健康和快乐。身高与金钱及健康不同,它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身材矮小,则说明这个群体在童年时代或者青春期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出现营养不足,一种原因是因为食物匮乏,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不够健康,各种疾病虽然没有夺走人的生命,却严重阻碍了其生长发育。就个体而言,身高受到基因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父母长得高,那子女一般也会长得较高。但是这种情况却不适用于一个规模庞大的人口群体,对于一个人口群体而言,实际上平均身高的差异就是营养水平差异的体现。以前我们认为,基因差异是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身高差别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原先许多国民身材矮小的国家如今都变成了国民身材高大的国家,而且不少国家的改变速度非常惊人。这就使得以前那种基因决定论遭到了抛弃。
如今,人们意识到童年时代的营养匮乏会产生长期的严重后果。身材矮的人收入比身材高的少,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如此,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里,也同样如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原因是人类的认知功能会随着人体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总体而言,长得矮的人就是不如长得高的人聪明。这样的结论当然容易被认为是对个子矮的人的一种污蔑,我的两个普林斯顿同事就因为这个问题而遭受了无数的邮件轰炸和来信指责,有的校友甚至要求校方将他们开除。但请容我在这里小心地对此加以解释。
在一个衣食富足没有疾病的理想环境中,不同的人会因为基因差别而出现身高差异,然而在认知功能上他们却不会存在系统性差别。但是在实际的世界,总有一些人会在童年时期遭遇食物匮乏问题,而这些人往往在身材矮小的人中占较大比例,这就导致了个子矮的人总体的认知能力偏差。营养匮乏可能只是由于没有摄入足够的热量,但也可能是因为过多地与疾病做斗争而造成了大量的热量流失。往往是一些特定的因素造成营养匮乏。比如,脂肪是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但是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脂肪摄入不足,而我们听说更多的却是很多人的脂肪摄入太多。
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不再忍饥挨饿时,营养匮乏现象就会减少。而卫生条件的改善、虫害控制以及接种疫苗的推广,也促进了营养匮乏问题的解决。但是,身材矮小的母亲很难生出高个子的孩子,即便只是考虑这点,我们也知道营养匮乏对身高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很多年。这种生物限制决定了人们身高增长的速度,所以,即便是营养已经改善,疾病也得以控制,一个群体也需要经过数代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身高增长上的潜能。但这并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可以避免身高短时间内过快增长所造成的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变得比以前高,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欧洲人的确比以前长高了许多。经济学家蒂莫西·哈顿和伯妮丝·布雷收集了11个国家的男性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身高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当时军队招募新兵时的测量,因此缺乏女性的身高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两位学者测算出当时欧洲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6.7厘米,而到了100多年以后的1976~1980年,欧洲人的平均身高增长到了178.6厘米。法国是这些国家中人口身高增长最慢的,平均每10年人均身高增长0.8厘米。荷兰则是最快的,每10年人均身高增加1.35厘米。其他的国家,人均身高每10年增长约1厘米。哈顿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是人口身高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收入的增长则是第二重要的因素。这一结论与本章的观点一致。伴随着食物短缺现象的消失以及卫生环境的改善,欧洲人的身高开始向从未企及的高度进发。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身高历史数据都不完整,但是通过大量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大量女性身高数据(近来这些调查也开始搜集男性的身高数据),获取了15~49岁女性的身高信息。由于人在成年之后与50岁之前身高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每个调查实际上给出的是出生时间跨度超过20年的不同年龄女性的平均身高数据。所以,这些数据不但能告诉我们调查时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通过对年轻女性与大龄女性的对比,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的身高在这20多年间的增长速度。在一些情况较好的国家,一般年轻女性要比年长女性高出1~2厘米。
图4–5显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身高变化。在图中,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的同一出生队列女性,它表示这个国家所有出生在某一年的女性的平均身高。横轴是人均国民收入,以对数标尺显示,每一个表示一国某一年份(比如1960年)出生女性身高的圆点,都与这一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值相对应。举个例子,在图中右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女性的身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而在这其中,出生较早的大龄女性,平均身高处在左下位置,而出生较晚的年轻女性,平均身高处在右上位置。美国的数据也在右侧,不过同欧洲人的比起来,美国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并不快。图的中间位置和左侧分布的是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女性数据。其中,几乎居于最左的深色圆点代表非洲人,它也说明在这些女性出生的年份,这些非洲国家的人民都十分贫穷。(注意在图中的右侧也有一些深色圆点,这些人均收入很高的女性数据来自加蓬。加蓬的石油出口提高了其人均国民收入,但实际上大多数国民仍处在贫困状态。)处在非洲人包围圈中的是海地人(白色圆点),他们多数都具有非洲血统,身高和收入水平也和非洲人相仿。中国(灰色圆点)也处于左侧。需要注意,这里的人均收入数据对应的都是女性的出生年份,时间则基本都是在1980年以前,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其人均收入比现在的要低不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多数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女性数据出现在图4–5的中间偏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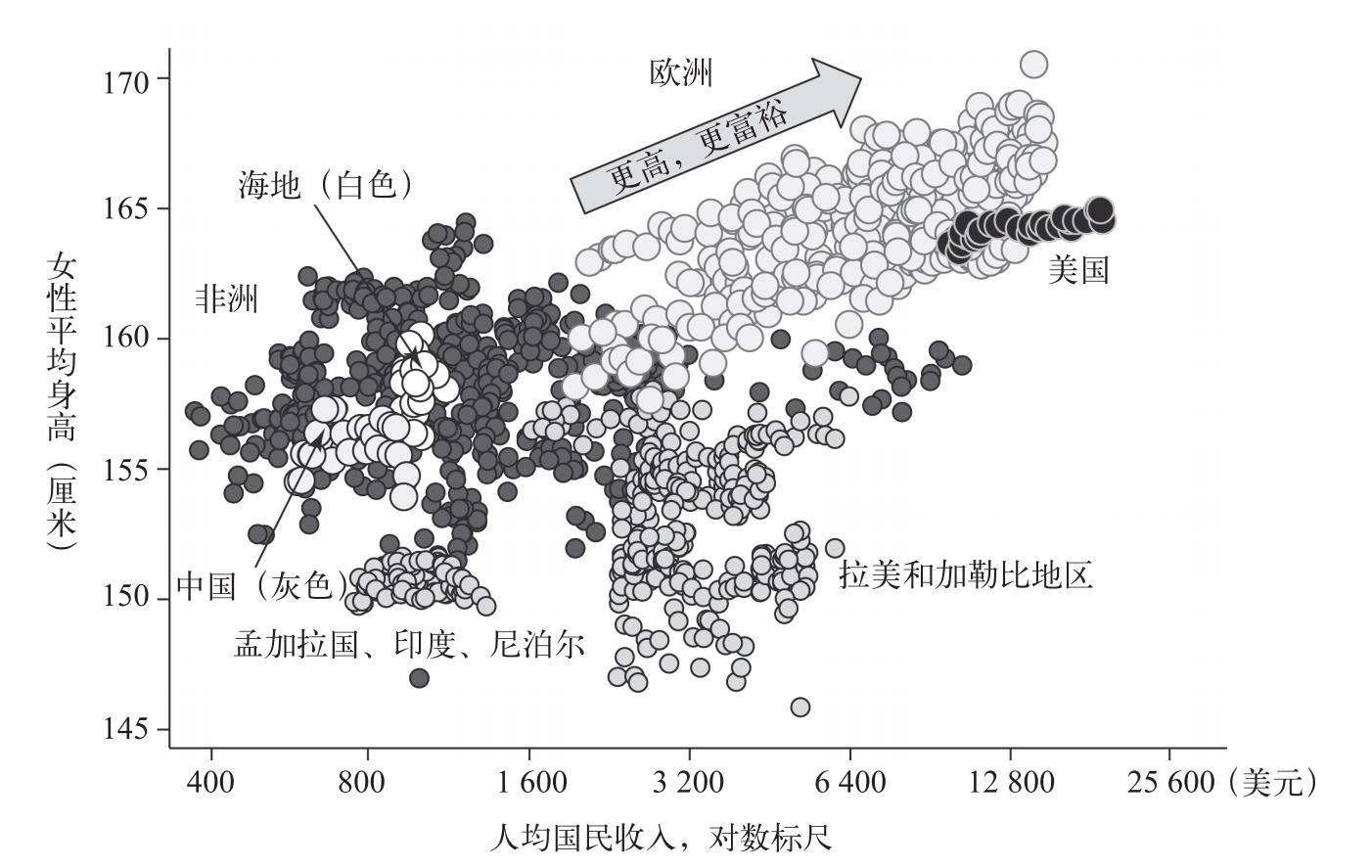
图4–5 全世界的女性身高
显示世界各地人均身高存在的巨大差距,或许是这张图最让人震惊之处。同是生于1980年,丹麦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71厘米,危地马拉女性的平均身高则为148厘米,此外,秘鲁和尼泊尔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50厘米,印度、孟加拉和玻利维亚女性的身高为151厘米。假设危地马拉女性的身高可以每10年增长1厘米,那么230年后,她们的身高才有可能达到丹麦人的水平。一个丹麦女性走到一群危地马拉的乡村妇女中间,会发现自己比她们整整高出一头,这简直就像是格列佛走进了小人国。
如果我们从图的左下看到右上,会很容易发现,富裕国家的人要普遍高于穷国的人。如果高收入也意味着更好的卫生条件、更低的儿童死亡率以及更充足的食物,那么这样的情况也算在意料之中。但若果真如此,事情也未免太过简单。假设我们现在把图中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去掉,就会发现身高和收入呈负相关:越穷的国家,人们的身高越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跟非洲人的特征有关。非洲人的身高其实并非一致,南苏丹的丁卡人身材高大,往往都是篮球运动员的料,而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希曼人则身材矮小。总体而言,非洲女性普遍较高,虽然和欧洲女性相比没有优势,但是同南亚人和拉美人相比身高优势却非常明显。这种收入与身高的负相关关系短期内很难消失,因为像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虽然近几十年经济增长迅速,新生儿童的身高却仍然相对较矮。
非洲人为何长得这么高?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遭受食物短缺,人们的饮食结构也相对合理,不像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吃得那么素。当然,不同的地区食物供给和卫生环境状况不同,卡拉哈里沙漠里的人肯定会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人们还是有肉类和动物脂肪摄入的。此外,非洲国家的儿童死亡率相当高,那些长得瘦弱矮小的儿童就更容易被死亡吞噬,如此一来,幸存下来的就都是长得相对较高的了。换句话说,在非洲这样的条件下,高身材的产生,是以高死亡率为基础的。只有瘦弱矮小的儿童大量死亡,幸存者有足够的能力克服恶劣的卫生条件所造成的发育不良,一个身形高大的民族才有可能诞生。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卫生条件。在那些随地大小便现象仍然普遍的地方,如果当地人口密度较高,那么儿童很可能因长期暴露于粪便细菌之中而发育不良。但是尽管非洲随地大小便的情况较为严重,但因人口密度较低,其人口发育情况比印度的要好。
很多非洲人比印度人长得高,也比拉美几个国家的人长得高。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身高不能作为衡量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也不能作为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的尺度。死亡率高低和收入多少是影响成年人身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两个关键指标。但是,绝不能因此认为,病痛和贫困会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人的幸福和身高。非洲人的例子已经证明,身材的高矮往往受制于饮食结构等局部因素。但是这些局部因素对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个群体的身高增长,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没有祖母的身高增长,就不会有母亲的身高增长,而没有母亲的身高增长,也就没有孩子的身高增长。今日人们的身高水平,除了受到目前的营养状况或者卫生状况影响外,也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再次提示我们,平均身高绝对不是衡量人们幸福与否的好标准。
南亚人身材极矮这一事实,或许是整张图中最具有启发性的部分。我们没有关于欧洲女性身高的历史数据,因此不知道现代印度女性的身高到底相当于历史上欧洲的哪个时期。不过,最新的印度数据包含了男性的身高数值,这些数值显示,出生于1960年的印度男性平均身高为164厘米——比1860年时欧洲男性的平均身高还要矮2~3厘米,即大约相当于18世纪时欧洲男性的身高水平。在所有的文献记载中,最低平均身高出现在1761年的挪威和如今的布希曼,为159厘米,而印度男性在1960年的数据仅仅比这个最低身高高5厘米。在锡金和印度东北的梅加拉亚邦,当地男性在1960年的平均身高甚至还低于159厘米。
印度儿童在20世纪中叶遭遇了营养匮乏问题,其严重程度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营养匮乏相比,甚至严重到如同人类狩猎采集时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情况。1931年,印度的人口预期寿命是27岁,这也反映出当时的营养匮乏是多么严重。即便是到了20世纪,印度人仍然生活在马尔萨斯的噩梦之中。正如马尔萨斯所言,死亡威胁以及食物匮乏会始终限制人口的增长,而即便是对幸存的人而言,生活本身也是痛苦不堪。这不仅是因为食物的数量不够,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也不充足。大多数印度人只能吃一些单一的谷物,还有一点点蔬菜,而铁和脂肪的摄入严重不足。为了活下来,哪怕预期寿命只有20多岁,印度人口的总体身高也不得不维持在低位,低到只有英国人17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要么死掉,要么变矮,“马尔萨斯魔咒”使得人们不得不做出权衡抉择。
如今印度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印度的儿童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矮最瘦的一群孩子,不过同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相比,他们无论是身高还是体格都有了进步,而消瘦症之类的情况也已经很少出现。印度人的身高在近几十年中逐渐增长,但增速却不及欧洲之前的水平,也比不上中国的水平。目前中国人的身高大约每10年增加1厘米,而印度人的身高每10年只能增长0.5厘米,这还是男性的水平,印度女性的身高增速更慢,大概需要60年才能增长1厘米。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印度女性身高的增速比男性的慢这么多,但应该和印度北部地区的重男轻女习俗有关,不过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印度南部比如喀拉拉邦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等地区就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于是这里的男性和女性身高同步增长。但是在北部地区,女性的身高增速就比男性的慢很多,而且这一地区男性身高的增速也不及南部地区。颇为讽刺的是,重男轻女这种歧视思想最终也对男性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论男女,都是母亲所生。而如果母亲长得过分瘦小,又缺乏营养,那孩子的体质和认知能力发展自然也会因此受到限制。
非洲人的平均身高在增长,但是在非洲某些地区却出现了女性变矮的情况。尽管我们知道富国的人不一定都会长高,但是从世界范围看,人的身高的确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增加了。欧洲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图4–5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样,在今日的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身高随着收入增长的趋势同样比较明显。由此倒推,非洲女性身高的下降恐怕和非洲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的真实收入下降有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比以前更长寿,物质生活更富足,同时人的体格也更为强壮,身高也在增长。这种身体的变化常常也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可能会随着身高增长而变得更强。不过和死亡率与物质收入的问题一样,身高增长在各个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按照目前的速度,玻利维亚人、危地马拉人、秘鲁人或者南亚人需要再过几百年才能长得和欧洲人一样高。与走在前列的国家和人民相比,有太多的国家和人民被甩在了后面,人与人在身体条件上的不平等越发明显。
[1] 《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2月出版。——编者注
18 世纪中叶之后,世界各国人口的寿命开始逐步上升,人类摆脱了致命疾病的侵袭与早夭的危险,生活水平也开始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健康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同步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终带来了一场人口寿命的革命以及物质生活的革命。这两项由相同的根本因素所推动的同步变革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并且延长了人们的寿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两项以差别扩大为特征的重大变革,“大分化时代”(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语)也终于到来了。经济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减少了贫困。虽然经济增长的成效很难量化(后面我将详述这一点),但是一项谨慎的研究估算,1820~1992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收入增加了7~8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84%降低到了24%。这是史无前例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平等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在18世纪,不平等多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地主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却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与各国间人口寿命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截然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现在也没有显出一点要缩小的迹象。
在这一章我将谈谈美国的情况,尤其是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的物质生活发展情况。之所以要在这里谈论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而这种引人注目的事实本身就可以很好地阐释本书的主题。当生活改善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受益,而正因为有人受益有人未能受益,所以生活的改进往往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距。不管怎么样,变化往往会带来不平等。是否存在不平等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该如何评价发展本身,比如谁受益谁受害,还因为不平等本身也有其影响。不平等可能让落后地区看到崭新的机遇,因此通常会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不平等也可能阻碍物质进步,甚至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不平等会启发或者激励后进者奋起直追,但是,如果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被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遏制,经济运行也会受到损害。
选择以美国为例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相关数据非常充分且易于理解。美元使用率极高,因此我们也不用换算汇率,美国的统计体系世界一流,它提供的数据非常可靠。如此便利的研究条件可谓奢侈,因为从整个世界的综合情况来看,这样的条件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并且,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历史数据非常不充分,因此要做历史比较非常不容易。比较19世纪和21世纪物质福利状况的不同之处,其难度之大,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比较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时过境迁,人们的消费模式不同,连价值标准也不相同,正如小说家L·P·哈特利所言:“历史就是另外一个国度。”而美国数据的充分,给予了我极大的工作便利,在这样一个我所熟知的数据环境中,我可以更好地阐述我的理念,厘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收入、贫穷与不平等问题做出的评价与分析。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生产总值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起点(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终点)。图5–1中,最上面的一条线展示了自1929年现代统计诞生以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总量的指标,是国民收入的基础。图5–1显示,在1929年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8 000美元,不过在1933年,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深入,这一指标降低到了5 695美元。在此之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路上行,尽管中间有数次短暂下滑,到2012年,这一数字还是增长到了43 238美元。这个数字是1929年的5倍多。需要说明的是,图中的数字都以2005年美元价格为基准进行了调整,以此我们就可以对真实的人均收入进行对比测量。若不做调整,1929年的美国人均收入实际为805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8 0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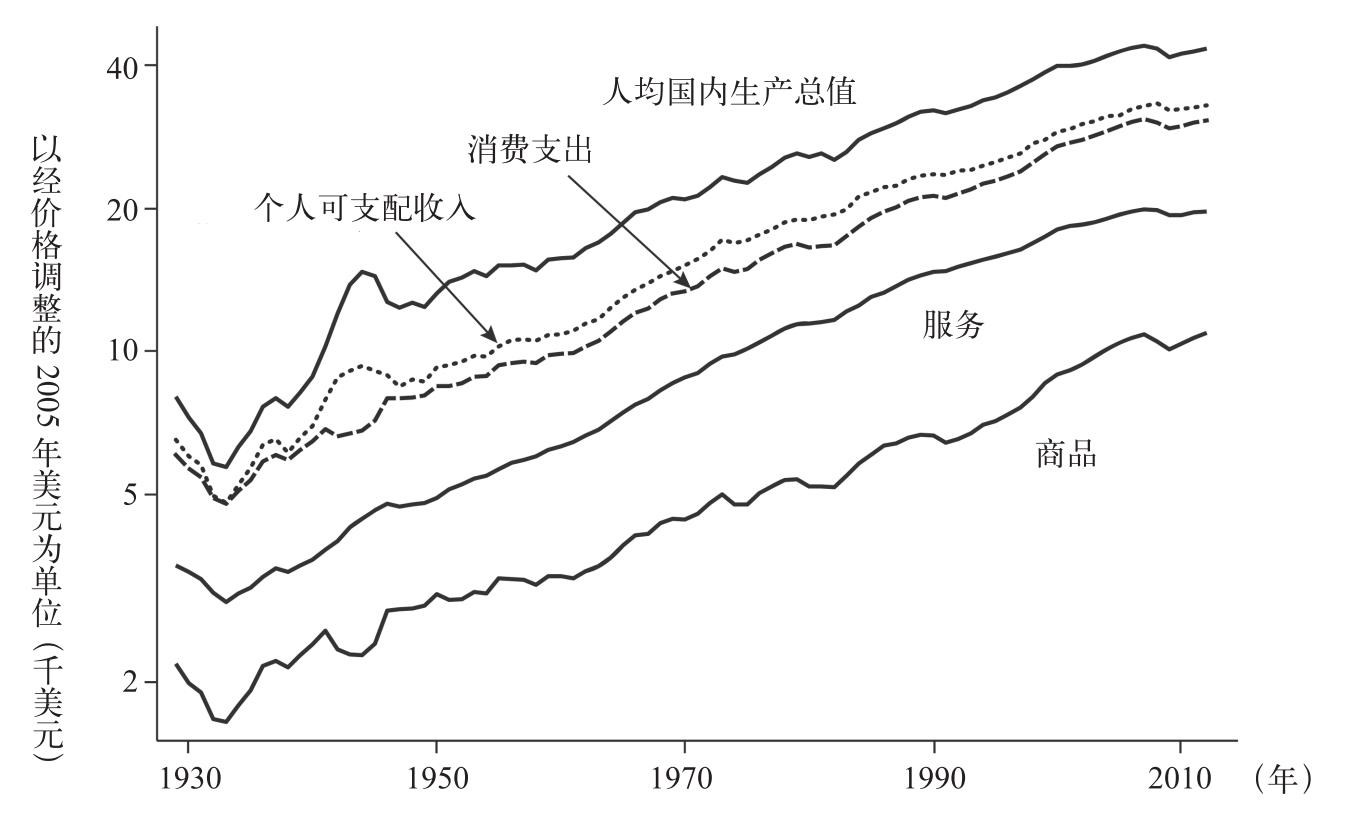
图5–1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1929~2012)
图中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倒退时即是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或者逆转之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的出现频率逐步减少,严重程度也越来越低——这本身也是经济进步的一种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虽然导致了大量人口失业,并且在本书写作之时仍未好转,但在此图中我们发现,它几乎未对人均收入构成严重的冲击。从1950年开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条线就接近一条直线,以每年1.9%的速度保持增长。而如果只算到2008年的话,它每年的增速更达到了2%多一点。尽管时间越往前推数据就越不稳定,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速实际上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并无大的变动。而每年2%的增长率,则意味着美国的人均收入可以每35年翻一番。以此计算,如果一对夫妻在35岁时有两个孩子,那么每一代的生活水平都会比他们的父母翻一番。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是看起来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那些几千年也未见生活改善,甚至生活经常出现倒退的祖先而言,这足以让他们震惊。不仅如此,这样的成就恐怕也会让我们的子孙们感到惊讶。
我们后面就会知道,国内生产总值不是一个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好指标,即便只是作为衡量收入高低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其局限性。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外国人在美国创造的产值,同样,最终归属于股东的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和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盈余也被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而在缴完税以及计算了转移支付之后归属于家庭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被称作个人可支配收入。图5–1中的第二条线表示的就是这一指标。从图中可见,个人可支配收入要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少一大截,但是它们的增长趋势和涨跌变化却非常相近。第三条线是消费支出曲线,虽然它反映的是花钱多少而不是赚钱多少,但是其变化趋势却和前两条线非常相似。个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差额,就是个人的储蓄额度。通过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储蓄额度一直在下降,尤其是近30年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是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现在的借贷可能比之前更为容易了;其次,以前人们需要储蓄以用于购房购车或者购买家电,但现在无须如此;再次,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降低了人们为退休而储蓄的意愿;最后,普通美国人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涨中获得了不少收益——至少一直到大衰退之前都是如此。
资本收益可以兑现消费,或可以让人们在无须储蓄的条件下实现财富积累。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储蓄就是收入和消费的差额,而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都是单位时间的流量。财富则非流量概念,而是存量,指的是某个时刻账户的总额度。财富会因为资本收益的增加或者减少而变动,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美国人的财富近乎缩水一半。财富也会随着人们的储蓄行为变化而变化。当人们增加储蓄时,财富增加;而当人们减少储蓄,或者由于退休、失业等原因支出比收入更多时,财富就相应减少。
图5–1中的另外两条线显示的是美国人的两大消费项目,一项是商品消费(在2012年占到了消费支出的1/3),另一项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中最大的两项,一项是住房和公用事业,这项消费大概为每年2万亿美元,约占消费支出总额的18%;另外一项是医疗保障,每年的消费额度约为1.8万亿美元,大概占到全部消费支出的16%。商品消费支出中,约1/3用于汽车、家具、电子产品等耐用品,2/3用于衣食等非耐用品。如今,美国人用于食物的预算仅有7.5%,如果加上在外吃饭的消费,食物的支出也不过13%。所有这些支出,都是体现美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项目,这些项目支出的增长告诉我们:伴随着寿命延长,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日益富足。美国人不仅寿命增加,生活质量也大为改善。
物质繁荣以及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个人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在内的各项衡量物质水平的指标,如今都受到了舆论批评。我们经常听说,消费过多并不能让人生活得更好,除此之外,宗教机构也经常就物质主义的危害向我们发出警告。即使是很多认可经济增长作用的人士,也对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式多有批评。国内生产总值没把很多重要的内容计算进去,比如家庭主妇的工作就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休闲活动也没有被计入;即便是很多被计入在内的项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计算。治理污染的成本、建设监狱的花销以及通勤的费用,经常被认为是不应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但是现在却都被包含在内。这类“防护性”支出,本身并非好事,但却是维护好事的必要支出。如果犯罪率上升,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建设监狱,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因此上升。如果我们忽略了气候变化,就不得不在灾害之后的治理和修缮上花费巨资,这样国内生产总值也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只计算维修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忽视了破坏的损失。
对于物质财富的分配,国内生产总值则完全无法反映。图5–1告诉我们很多物质财富增加了,却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得到了这些财富。物质财富分配的定义与衡量框架都非常重要,我之后会加以详谈。财富分配的结果是至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一章,我们也会大篇幅谈到。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首先要驳斥那些认为物质水平提高对增进人类幸福贡献甚少或者没有贡献的说法。我要强调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
要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各种投资。首先是对物的投资,比如铸造机械、修建高速公路或者宽带等基础设施;还有对人的投资,即为更多人提供内容更多质量更好的教育。知识需要得到认识与拓展。知识的拓展或是新基础科学的产物,或要归功于工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向服务和商品的转化,还可能来自于设计的不断改进与更迭。正因为有了知识的拓展,汽车工业才能从福特T型车发展到今天的丰田凯美瑞;也正是因为知识,我1983年的那台笨重的电脑早已换成了如今外观圆润轻薄、内在功能更为强大的笔记本。对研发的投资促进了创新的流动,但是,新观念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知识的供给也已经国际化,而不仅仅是在一国之内,新的理念可以很快从诞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创新也需要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到将新科技转化为产品、服务的商业赢利模式。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这一切很难实现。创新需要得到产权保护,而这就要求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以处理纠纷,保护专利,而相关的税收也不能过高。当这些条件都实现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就会随后出现。这就是过去一个半世纪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底价值何在?答案是,除了让我们摆脱贫困以及物质匮乏,新的商品与服务还把很多之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而这些新的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家用电器的使用,把人尤其是妇女从枯燥的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在以前,人们每周都要拿出一整天来洗衣服,先用燃煤烧开的水来浸泡衣物,然后用双手尽力搓洗,之后还要将衣物挂到外面晾干,最后还要收回来熨烫。20世纪50年代,苏格兰的一则洗衣粉广告语就是:“每周都为你节省洗衣用煤。”古罗马人已经拥有自来水和良好的卫生条件,然而只是在近代,人们的收入增长之后,这些才为更多的人所享有。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拓宽了居所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娱乐活动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和亲朋好友更加方便地聚会,而这也正是那些反物质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飞机的出现让许多人得以有机会前往国内各地以及世界各地。我们可以全天候和孩子或者朋友保持联络,也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还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当代或者古典的文学、音乐以及电影。互联网创造了信息与娱乐的盛宴,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免费的。新的医疗手段,比如像上一章我们提到的降压药,使我们延年益寿,有更多时间去享受各种可能性。而其他的医疗手段,诸如髋关节置换以及白内障手术则降低了阻碍我们充分享受这一切的风险。即便是现在我们的医疗支出过多,也不能否认医疗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进步。没有人否认经济增长有副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益的。
依照某些人的看法,我这里对物质创新贡献的罗列可谓老生常谈,甚至连老生常谈都不算。但无论怎样,我这里的所列所举足以说明,那些认为所有进步都对人类的幸福毫无意义的说法,或者那些认为我们只是为了和邻居攀比而追求物质生活提高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会说,尽管图5–1提供了大量的增长数据,但还是有证据表明美国人没有比半个世纪前过得更幸福。这样的发现和我们所宣称的经济增长有益不是矛盾吗?当然未必。在第一章我们就提到,人们过得是否幸福,跟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是否满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一章的图1–7就显示,虽然丹麦人和意大利人觉得自己的物质生活比孟加拉人或者尼泊尔人要好很多,但是他们过得却没有后者幸福。美国人对自己过去100年的物质生活变化做何评价?因为没有相关数据,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收入分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图5–1中的数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家庭的真实情况相比,的确有过分夸大之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普通家庭的真实收入并没有在图中得到真正的反映。这里的问题是,并非美国人对经济的大幅增长不满意,而是因为经济本身增长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增长。因此,人们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幸福,也就不足为奇。
收入增长增加了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因而是有益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像图5–1这样的指标还是有缺陷,有些事情未能得到反映。比如娱乐休闲时间完全没有被计入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如果人们决定减少工作量,多花时间在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就都会下降。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不如美国高,一个原因就在于法国人的假期更长,但是假期长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就一定是坏事?这当然没有定论。很多未进入市场的服务内容也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比如女性在家做全职太太,她的全部相关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如果她是在其他人家里做工,她的劳动就会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如此一来,人均收入肯定会上升。再比如,互联网以低成本为大众提供了更为优质的娱乐内容,休闲生活的质量也得到提升,但是这些却都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诚然,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式有其合理性(有些是出于技术考虑),但是如果将其作为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指标,则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我们之所以对休闲娱乐未能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感到担忧,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人的时间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如今的女性,尤其是和高学历男性结婚的女性都开始外出工作了。如果我们认为休闲是好事,而工作是坏事,那么这些女性加入就业大军本身只能说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得不从事两份或者三份低收入工作的女性而言,外出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意义重大。不过,对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只看到人们收入数字的增加而忽略了他们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等问题,那就显然过分放大了这种外出工作的益处。对很多女性而言,外出工作使她们获得了半个世纪前的女人们无缘体会的心理愉悦。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将那些失业人群的“休闲”看成好事,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多项研究也已证明,失业者往往是对自己的生活最不满意的群体之一。所以,不能因为任何对休闲娱乐价值的考虑而对图5–1的数据做出机械调整。
2/3的美国居民都拥有自住房,因此无须缴纳租金。但是住在自己无须纳税的房子里,也算是得到了一项有价值的服务,因此这项服务也会被计入消费者支出、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实际上,按照核算人员的逻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相当于给自己支付房租,所以他们把这部分的大多数资金(2011年约为1.2万亿美元)都计入了收入和支出。这看起来像是“想象”出来的收入,但英国政府就曾一度对这种“想象”出来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我记得当年税务账单送来的时候,我那一向奉公守法温文尔雅的父亲也冒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反政府情绪。虽然今日的政府可能意识到存在问题而放弃了这项收入,但是核算部门将这部分纳入计算却也是对的。这其实反映出,对于某些项目是否应该算作收入,普通人和核算部门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个人收入和支出中也会包含政府以消费者名义支付的医疗费用,但是出于复杂的技术原因,政府为个人教育所支付的费用没有被纳入收入支出的核算中。
如果有政客跟你说,“你现在的生活水平真是前所未有”,而你自己的感受是,“哪有?反正我没觉得”,那么,对于他们给出的所谓生活变好的理由,比如你付给自己的房租上涨了,或者是政府给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你肯定不会买账。
医疗保障上的支出几乎和住房支出的规模一样庞大,但是要评价这些支出是否物有所值,却困难许多。医疗保障上支出了多少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却很难完全说清楚。如果医疗保障是跟金枪鱼罐头或者iPad平板电脑等一样在市场上售卖,那么它们的价值就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的支出来计算。但是,医疗保障费用在美国主要是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支付的,因此这些费用支出到底对人起了多少作用根本说不清楚。经济核算人员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以医疗的开支衡量医疗的成效。有的人因为医疗的成效远远超过了医疗花费,认为以支出衡量成效低估了医疗保障的作用,但相反的观点则把讨论重点放在了医疗费用的浪费上。双方争执不下,唯一没有争执的是医疗保障的效用的确没有很好的评价标准。
我之前肯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之时,曾经大量列举新商品的重要性,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商品尤其是那些具有极其崭新概念的商品的价值,并没有被很好地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同时,现存商品的质量也在提升,比如,现在的衬衣免熨烫了,手机有了语音识别功能,车的安全性能提升了,电脑的运行速度更快了,但是这些质量提升所产生的价值也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核算。国民经济核算人员肯定考虑到了这些方面,但也的确想不出如何将它们更好地反映到经济核算中。有些经济学家称,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多商品的生产,比如房子比以前多了,衣服比以前多了,桌子椅子比以前多了,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但如今经济增长更多意味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不过,衡量质量提升的价值要比计算数量增长困难得多,而时代越发展,统计人员在进行经济核算时出现的遗漏也可能越严重。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像图5–1那样仅以数字增长来评价美国人的生活情况肯定会造成低估,但他们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对此加以修正。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比以前的好。比如,自从有了ATM(自动取款机),人们的确是不用再每次都往银行跑了,但若想到是贪得无厌而且误入歧途的银行借贷导致了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那么,银行系统是否更加善待了消费者这个问题,就非常值得考虑。
如果说物质改善是一个金苹果,那么这个金苹果里还隐藏了一条蛀虫。从图5–1中就能看出,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正在减缓,现在两代人之间的生活变化也没有过去的那么大。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对1970年前后的变化趋势加以对比,就会知道即便不考虑最近几年的大衰退,这种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趋势也依然明显。在图中,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清晰可见。在1950~1959年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3%的速度保持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增速提高到3.0%;70年代,增速为2.1%;80年代,增速降低为2.0%;90年代,增速降低为1.9%;21世纪最初10年,增速则直接下降到了0.7%。即便除去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21世纪最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只有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从3.0%降低到1.6%看起来差距不大,但如果从复合增长率来考虑,则意味着原本25年的时间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倍,而现在则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50%。经济持续扩张意味着人们的收入会持续增长(至少有这个可能性),而如果经济扩张得较快,则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矛盾就不会显得那么激烈,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在无须别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利益。
从数据上看,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趋势的确很明显,但是,如果真如之前所说,很多商品与服务的提升未能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则这种下降趋势就有可能被夸大了,或者根本不存在。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中,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服务本身比较难测算,所以,核算人员在这方面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遗漏。此外,互联网领域的新产品或者电子商品是近来才出现的,它们在提高生活水平上的价值还几乎没有被完整地反映到经济核算中;医疗保障的效率越来越高,而它们所带来的寿命增加也没有被有效纳入核算。当然,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要注意也存在很多矫枉过正的现象。在第四章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寿命的增加有的是源于医疗保障服务的改进,有的则只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变化;比如人们停止吸烟也会促进寿命的延长。所以,如果我们要将寿命增加赋予价值,则这部分价值将非常难以计算,并且一旦将这部分价值都归因于医疗支出的增长,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就会大大提高,而这是不正确的。这再一次说明,改进后的统计方法有可能比原有的统计方式有更多弊端。不过,并不能因为现在的统计方式存在低估某些进步的问题就不予讨论,在本章的后面我将继续阐述这个话题。
要想了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对其最贫困人口的影响,只需观察一下美国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图5–2展示了官方公布的贫困率变动情况,这些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的统计,图中底部加粗的线表示美国人口整体的贫困率。1955年,这一数据为22%,到了197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1%,此后该数据就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0年,美国的人口贫困率为15%,比金融危机前的高出2.5个百分点。暂时忽略人们对贫困率统计方法一直以来的批评,我们会发现,至少从表面上看,图5–2展示的美国贫困率变动情况与图5–1展示的物质水平进步情况有着极大的矛盾,尤其是在1970年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之后的部分,其矛盾更为明显。197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停止,从1973年到201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超过60%;但是,这些增长并没有对贫困率的下降产生任何作用。无论人均收入增长到了何种程度,被官方定义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都未被惠及。当然,这里的确存在一些统计方法上的问题,统计贫困人口的收入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收入指标并非一致。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没能解决其贫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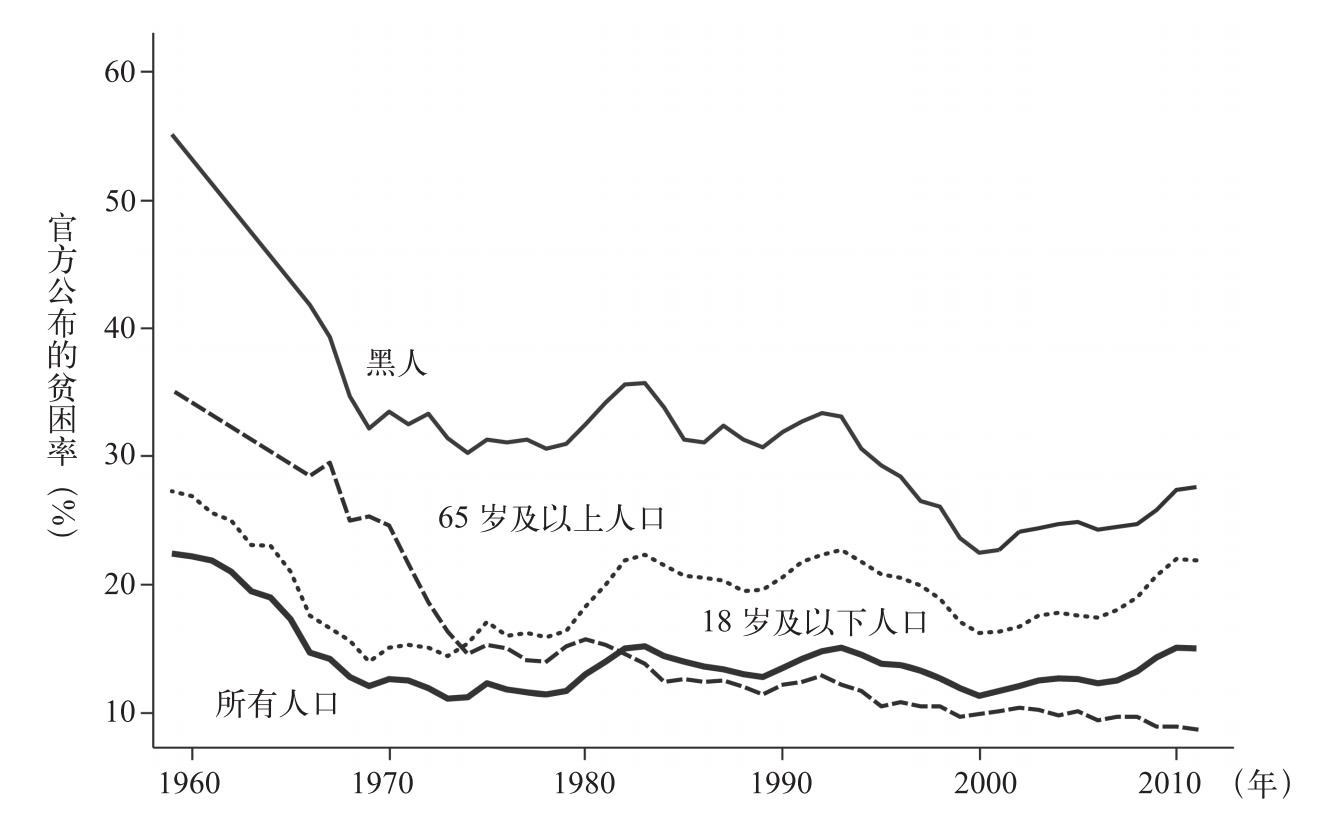
图5–2 美国的贫困率(1959~2011)
在美国,不同群体的贫困率存在差异,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数据显示尤其如此。截至目前,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图中未显示)的贫困率最高,而老年人的贫困率最低。当然,这三个群体的贫困率实际上也在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数据统计的早期,下降程度更为明显。老年人贫困率的降低常常被归功于美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保证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退休金会根据物价变动进行调整。儿童的贫困率要比成年人的高,并且和其他群体以及整体的贫困率一样,儿童贫困的程度在过去30年也没有明显下降。我们要注意,图中展示的只是贫困率,而由于人口总数一直在增长,因此贫困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速要远远高于贫困率的增速。到2011年,美国有4 620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在1959年,这一数字仅为670万。
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却在增加,或者说得好听点,贫困率一直停滞没有降低,这是否可信?数据的计算是否存在问题?当然应该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什么人可以被认定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基础理念非常简单,但如何在现实中实施却大有学问,其中最为棘手的包括如何确定贫困线,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地更新贫困线。
美国人口贫困线划分开始于1963~1964年,由当时在社会保障总署任职的经济学家莫利·欧桑斯基划定。欧桑斯基对一个四口之家(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每天所必需的食物费用进行了统计,而因为当时一个典型家庭会把1/3的家庭收入用于食品,因此,欧桑斯基将统计的结果乘以3,就得出了当时的贫困线水平。1963年,贫困线被定在了年收入3 165美元。1969年8月,这一数字被采纳并确定为全美的贫困线,此后,除了根据物价水平做出调整,这一贫困线再也没有变动过。2012年,这一贫困线的最新数字为23 283美元。半个世纪间,对划定贫困线不做任何方法上的改变是非常奇怪的,为何我们不在遵循原来理念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贫困线划定方法进行调整呢?但现实就是如此,1963年的贫困线划定方法如今仍在使用,除了考虑通胀水平之外,未做任何变更。
欧桑斯基的贫困线划定方法以冠冕堂皇且引人注目的营养需求为出发点,并做了所谓“科学化”的延伸,但科学化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当时的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向贫困宣战”计划,政府内的经济学家需要有一条贫困线作为依据,他们觉得3 000美元这个数字很合理,于是就计划将贫困线定在这个数字上下。欧桑斯基当时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近乎凭空想出来的数字寻找依据。最初,她倾向于采用农业部的“低成本食物计划”作为贫困线划定依据,但这个计划需要人口每年的收入超过4 000美元。最终她选择了标准仅为3 165美元的“经济食物计划”作为贫困线划定依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后者更稳健或者更具有科学性,而仅仅是因为3 165美元这个数字更接近最初设想的3 000美元!
讲出这段故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约翰逊政府经济学家的虚伪,更不是要抨击一位杰出公务员的科学诚信。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政府官僚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的:贫困线本身的确需要看起来合理,且易于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接受。实际上,当时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为的合理贫困线也在3 000美元左右。以食物作为说辞的贫困线划定依据非常合适,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贫困和挨饿是一回事,要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贫困。以营养学为基础的计算也让这条贫困线看起来更加“专业”。但实际上,除了贫困家庭本身,专业人士不会知道一个贫困家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1963年贫困线初次划定之时,政府宣传的需要与现实需求相差无几,因此这条贫困线也便于采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人们对贫困线的更新产生路径分歧的时候,对新贫困线的划定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如果半个世纪前欧桑斯基划定贫困线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新的贫困线就应该以新的经济食物计划为基础,设定新的乘数,并在每年予以重新计算。而如果我们认可盖洛普调查,就应当以公众的意见作为贫困线更新的标准。(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如果我们要对贫困人口做出界定,并且对他们予以不同的食物补贴等,那么在设定贫困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他们的意见,因为对贫困人口进行补助等方面的资金,都是来源于他们所缴纳的税款。)但实际情况是,以上两种观点皆没有被采纳。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技术修订,以及根据物价上涨水平做出的调整,今日的贫困线与1963年欧桑斯基(或者说是约翰逊的经济学家)所划定的那条贫困线别无二致。欧桑斯基本人在这些年也不断呼吁对贫困线的设定方法进行调整,但如果按照她的思路,今天的贫困线可能会比现在所采纳的这一数字要高出许多。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人们认为现在的贫困线早就应该上调了,起码应该和真实工资的上涨速度一致。以上两种意见,无论采纳哪种,贫困线标准都会随时间推移而上升,同时贫困比例的增长速度也肯定会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更快。我们的确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增长未能有效减少贫困是因为贫困线不合理,但是现在来看,如果对贫困线进行合理修订,则只是更加证明了美国经济增长没能够有效消除贫困。
如今,美国的贫困线已经变成了一条绝对贫困线,这样的贫困线不会考虑其他人拥有什么,也不会考虑经济生活的通行标准。当存在“一篮子”可以明确保证人们存活的必需品时,这样的一条绝对贫困线是有意义的,它只需要保证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这“一篮子”必需品就足矣。而除了要考虑物价变动因素,以保证这一贫困线收入永远可以支付这“一篮子”必需品之外,这条线也永远不需要加以改进。这样设计贫困线,在像非洲或者南亚地区那样的穷国还可行,对美国则不合理,美国贫困家庭的贫困问题绝非以吃喝为中心,即便在1963年,他们的需求也不仅仅是3 165美元那么简单。美国人真实的贫困境遇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家庭和儿童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邻居或者朋友们那样体面的生活。无法体面生存是一种绝对的贫困,而要摆脱这种绝对的贫困就需要收入达到当地的一定水平。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设置相对贫困线的合理性不言而喻。而一条相对贫困线意味着,同1963年相比,美国的贫困水平和贫困增长速度都被低估了。
在一个总体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的世界里,绝对的贫困线意味着在这条线之下的穷人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的贫困线也是进行一系列福利和补贴分配的标准。如果这条线不能跟随社会的进步而改进,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福利就会越来越被限定在一个更狭小的人群范围中。
贫困线不能更新只是美国在贫困统计上的缺陷之一。另外一项缺陷是官方统计常常通过税前收入和补贴来判断某个人是否贫困。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缺陷。很多政府济贫项目,比如通过税收体系支付的食品救济券(官方称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现金补助,在统计时都被忽略了。这就使得这些政策产生了荒谬的结果,即无论这些行动对于减少实际贫困起了多大的作用,都无法在统计上降低贫困率;无论政府在此类消灭贫困的战略中显得多么有创造性,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官方统计都永远显示不出这些努力的成果。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缺陷理论上能够避免。实际上,如果对收入的统计能够更为宽泛,那么2006年以后的美国人口总体贫困率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增长幅度。同样,这样的失败不能归咎于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人员。这项缺陷在很久之前就广为人知,而人口普查局也在积极研究更为可行的统计方法。缺陷产生的主因在于原有的统计方式没有考虑补贴或者税务减免,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63年这两种情况都还不存在,当时极少有穷人纳税,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无关紧要。而到了后来,则是一切政治挂帅,要想对统计贫困人口的方式做出任何调整,哪怕是修补一个人人都了解的缺陷,也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困难、争议以及党派纷争都接踵而来。正因如此,几乎没有一届政府动过修改统计方法的念头。
那么,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贫困率情况到底如何?鉴于我们对处在分配底层的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即便是官方的贫困线划定本身存在缺陷,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从1959年一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的总体贫困水平在下降当然毫无疑问,老年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外,7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人口贫困率降低的速度放缓甚至停滞也是事实。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据政府所实行的固定贫困线,贫困率变化确实陷入了停滞。
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负面结论,则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加以反驳:因为质量提升和新商品未能被有效地纳入统计之中,所以在减少贫困上很多进步被低估了。而这意味着通胀水平也被高估了,因为价格上涨并非只是因为商品价格变得更贵,还因为某些产品质量提高了。如果真是这样,贫困线标准的上涨就太迅速了,那些被不断纳入贫困人口的人也就根本不算穷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贫困人口到底可以从这些无法统计的商品质量改进中获益多少,但是,如果认为以上的论点成立,那么我们现在肯定已经战胜贫困了。同样,官方统计中没有包括旨在帮助穷人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也会造成对贫困减少成效的低估。事实上,官方的这些做法不仅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实际贫困率(我们已经从最近的这次经济衰退中看到这一点),在长期也会大幅度降低贫困人口的比例。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赞成的方式,让贫困线随着整个人口平均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而相应变动,那么美国人口贫困率在过去的40年中可能会大大增长,并和经济的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得更宽泛些,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成果被广泛分享。但70年代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也再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战后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段是增长相对较快且被广泛分享的时期,另一段则是经济增速放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的时期。
世界其他各地统计贫困问题的方法,包括整个世界对贫困情况的统计,都和美国有类似的问题。如何划定贫困线,一直争议不断,而如何定义收入并对其进行统计,也是一个长期的技术性难题。变更贫困线是极为困难的事,因为各国存在思维或者政治上的差异,更因为对穷人定义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某些福利的改变,有的人会因此获益,但也有些人会因此利益受损。任何针对贫困的计算方法变更,哪怕仅仅是修订一个明显且尽人皆知的错误(比如没有将食品救济券纳入统计),也会在政治上招致反对。对贫困的统计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防止人们落入贫困等方面,都必不可少,它是社会公平体系的重要一环。对贫困的统计,也意味着国家将消除贫困及其后果视为自身的责任。正是通过对贫困的统计,各个国家才真正得以了解本国的贫困情况;同时,按照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经典说法,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以国家的视角去看待它”。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没有统计就谈不上统治,没有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统计。统计中的“统”也是统治中的“统”,这不是偶然的。
收入的变化情况可以从发展、贫困和不平等这三个角度加以考察。发展事关人均收入及其变化,贫困事关底层人的生活,而不平等则主要是指家庭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收入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创立的一项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值在0到1之间。当基尼系数为0,意味着绝对的平等,即人人收入平等;反之,当基尼系数为1,则意味着绝对的不平等,即所有的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人完全没有收入。这个指标所衡量的是收入偏离平均值的程度。(具体地说,基尼系数就是平均差除以平均收入的2倍,即相对平均差的1/2。举个例子,如果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就是平均数的2倍,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是1,而如果这两个人的收入一样,则他们之间的差是0,基尼系数就是0。)
从“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较为稳定,但此后开始上行。对于收入最高的那10%人口而言,这个现象也同样存在,而且税前税后皆是如此。在低收入者收入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平均收入却在增长,这只能说明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却无助于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全部收入进行考察,弄明白它们为何增长以及是什么促进了它们的增长。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一两项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清楚。美国人的收入就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如果我们只知道平均的水流速度,就无法弄明白那些旋涡或者平静的水面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图5–3显示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变化情况。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人口普查局都会就前一年的收入情况展开家庭调查,最新的一次调查是在2011年3月进行的,收集到了87 000个家庭在2010年的收入信息。该图显示了所有6档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按2010年价格水平调整,并以对数标尺标示)情况,最上面的一条线表示收入顶端那5%家庭的平均收入。1966年,顶尖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处在后2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11倍。到了201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接近21倍。这些都是税前与受到补贴之前的数据,并且不包含医疗保障等政府提供的各类津贴。这种计算方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与图5–3不同,图5–1的收入数据中包含了这类津贴,这也是为什么从图5–1看,我们生活的改善情况似乎比图5–3所显示的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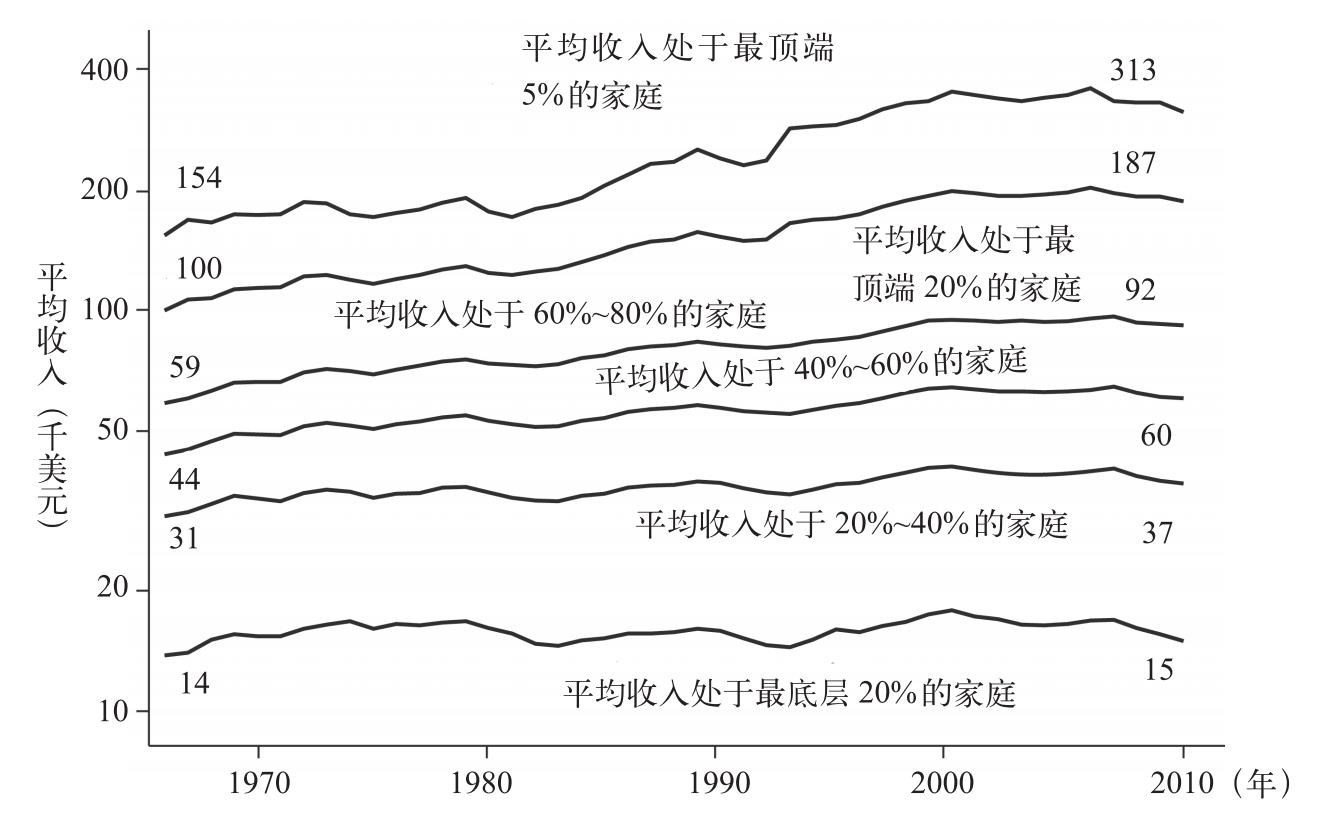
图5–3 美国家庭收入的分配
这张图显示出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情况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所有类型的家庭收入都在增长,但此后的收入增长开始出现差异。通过之前关于贫困人口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处在最底层20%的家庭收入增长非常少。在过去的44年中,它们的平均收入年增长率不到0.2%。即便是在这次经济衰退之前,它们的真实收入也没有比70年代的水平高。而那些处在收入顶端20%的家庭,它们的平均收入却以年均1.6%的速度在增长。但这个速度还是比不上收入最高的那5%的家庭——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年增速达到了2.1%。当然,如果考虑到那些难以测算的质量改进所引起的生活变化,则最底层那20%家庭的收入增长实际上要比这里显示的情况要好。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收入顶层家庭和最底层家庭在收入增速上的明显不平等。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张图存在两个缺陷:首先是它的时间跨度不足;此外,调查样本太小,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例如盖茨和巴菲特就未被包含在内。在后面我会重点说一下这些缺陷,但还是想先把重点放在这过去的40年间,那些一年也挣不了几万美元的广大民众身上。
考察收入问题,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毕竟多数家庭的收入是靠工作得来的,因此工作和薪水在家庭收入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劳动力市场又并非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很多人,比如家庭主妇、退休人员、儿童、失业者或者残疾人,都没有工作收入,他们的生存或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或是依靠养老金以及政府补助。有些人以经营企业来生存生活,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是劳动所得,一部分则是来自对企业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存主要依靠自己或者家族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分红或者利息。
很多家庭中经常有不止一位工作赚钱的成员,所以家庭的人员结构也影响了个人收入转化为家庭收入的方式。这就是收入分配的人口特性效应。有的家庭是男性在外工作而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他们的收入特点与那些拥有顶级收入的权势夫妻相比大不相同,这类人口特性的差异一直是不平等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政府的政策也影响深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决定所得税的比重,制定社保、医疗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会推行多种针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与监管举措。政治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之间的冲突,政府则是选民、利益集团以及维护代理人利益的说客们的必争之地。工会、老年人、移民,甚至囚犯群体的规模和力量大小,都会对收入分配的变化产生影响。而这一切的背景是,科技、国际移民与贸易以及社会规范都在不断变化发展。
收入分配绝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种机制的作用。比如,单纯的劳动力市场供需或者基尼系数这样的衡量指标都不能有效地解释收入分配。实际上,收入分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政治、人口特性,包括历史也在起作用。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简·丁伯根就认为,收入分配的演变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现,也不取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而是技术发展与教育之间的一场竞赛。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与克劳迪娅·戈尔丁曾使用这一论断来描绘美国劳动力市场近来的发展情况:技术在工作中的运用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技能、接受相应的训练或者至少需要对这种技术进行适应,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需要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如果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教育的价格就会上升,而那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工人,其收入也会领先于其他工人,于是收入的不平等就会扩大。相反,有些时候,比如当越战导致不想服兵役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学时,受教育的需求就会跑到技术需求的前面,于是,技能的供给就增加了,技能的价格就会出现下降,这时候人们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就会缩小。
在20世纪初期,人们主要的教育水平差别不过是高中毕业与否;而如今,教育的平均水平已然大幅提高,现在的差别是看有无大学学历。生产技术的发展也使得高技能人才更受青睐,这种趋势被称为技能型技术进步。以前,技术的升级不过是从农场作业变成流水线作业,如今,技能升级看的是你有没有写代码的能力,有没有执行创新任务的能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者会更加善于利用新技术,而在新技术的适应、改进以及调整等方面,他们也有更强大的能力。
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一直都在提高,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给也一直在增加。如果其他方面没有变动,这种持续的教育发展早就应该降低了教育的价值,并且会使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更是如此。当技能供应增加的时候技能价格还在上升,这只能说明社会对技能的需求度上升更快。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上升主要是因为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技能提升提出了持续不断的需求。他们相信,在过去30年中出现的技能型技术进步升级,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引擎。不断更新的技术变革,使得年轻人相信上大学的回报会越来越高,而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则说明人们已经对这种趋势做出了行动上的反应。
电脑、互联网以及信息产业等方面的快速变革,使得市场更需要能利用信息制定决策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相关人才,但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教育的发展就无法跟上这种市场需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趋势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教育系统变得足够灵活,能够在技能培训方面实现与需求同步,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增长就将被终结。
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来不是某种从天而降的科学突破所引发的,也不是某个孤独天才的灵光一现,它通常是对经济环境或者社会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有些时候,基础科学已经提供出研究成果,而其前景也清晰可见,但是如果企业家或者工程人员无法找到相应的商业模式与赢利机会,那么它们就只能被束之高阁。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就曾指出所谓定向技术变化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只有具备充足的技能熟练劳动者,很多新技术新方法才可能得到采用和发展。他认为,不能说是“越战”所引发的技能提升催生了电脑的发明,而是早期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技能溢价,激发了更多人去接受大学教育,而大量具备高学历的劳动者的出现,则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并进一步抬高了技能溢价。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在信息技术领域所有的革新都完成之后才会停止。但是,创新的焦点又会很快转移到其他的领域。就像以前我们的创新点从铁路转向汽车,又从汽车转向电子产品那样。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不过是这一种创新机制的副产品,并在技能的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说,虽然不平等本身是非常不好的,但它又作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提高了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用家庭激励为例来理解不平等现象。在家庭生活中,当父母对乱糟糟的房间终于忍无可忍时,就会采取将子女的零用钱数量与房间整洁度挂钩的激励方法。这样的办法一般都会奏效,结果是房间的确更干净舒服了,父母因此更舒心,孩子们也享受到房间井然有序所带来的益处。但是,这也会产生一些风险。如果一个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得到物质奖励,或者有的孩子就是天生比其他孩子更爱干净,那么最初大家零用钱一样的情况就可能被打破,并变得不平等。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中,所有的孩子都会保持房间的整洁,并得到同样的零用钱。但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差异化的激励制度会造成零用钱数量上的不平等。有些父母或许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毕竟每个孩子都享受平等的机会,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但是有的父母可能对此敏感,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在整理房间、保持清洁度方面的天生能力并不相同,每个人也都会犯错,因此就可能认同某些孩子的看法,认为这种新的不平等其实并非公平;机会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总是完全公正。
如果这种家庭激励模式持续的时间足够长,而同时孩子们又会将自己得到的零用钱进行储蓄,那么,不平等就会进一步加大。即使所有的孩子都存入比例相同的零用钱,但因为各自零用钱的数量有别,有的孩子就会比其他孩子存得更多,逐渐地,他也会变得比其他孩子更为富有。储蓄扩大了因零用钱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导致了财富的不平等,而这种新的不平等,会让最初的零用钱差别变得不值一提。真实的经济生活也是如此,财富的不平等会让收入差异看起来微不足道。如果那些天生就善于保持清洁的孩子,同时也天生善于积累财富,那么,不平等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在真实的社会中情况也类似,如果那些着眼于长远且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同时也善于学习且倾向于将知识收益进行积累,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发展速度也会因此更快。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整个国家,在激励与不平等之间,总是存在着深深的矛盾。
新技术的发明和进步是否真的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了?对此持肯定看法的人,大概认为更好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有更多的产出可用于潜在分配,所以即便是技术溢价增加了,那些没有掌握技术的人也不应该因此而收入降低。图5–3便显示,收入处在最底层20%的人群,其家庭收入并未出现下降,然而,这张图并未反映出个人最低工资在下降的现实。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长,是因为有更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所以每个家庭能赚钱的人数实际在增加。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个人工资的下降?
全球化被认为是个人工资收入下降的一大原因。很多商品原本是交给美国本土的低技能劳动力来生产的,然而现在却被逐步地转移到了贫穷国家,许多公司甚至都已经将后勤服务工作(诸如索赔处理)和客户服务中心转移到了海外。移民和非法移民也经常被认为是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下降的原因,然而这样的罪名却充满争议。不少可信的研究已经指出,移民对这部分人收入的影响其实很小。医疗服务成本上涨也是大部分劳动者收入没有提高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劳动者的健康医疗保险支出是其总体收入支出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很多研究所证明的,劳动者总体收入增加的那一部分最终并没有变成工资,而是转移到医疗支出上了。实际上,医疗保障支出增加得越快,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长就会越慢,反之,如果医疗支出增加得较慢,则工资增长就会相对较快。1960年,医疗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5%,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增加到了8%,而到2009年,这一比重则大幅增加至近18%。
低技能工作者的收入也因为他们具体技能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收入状况最差的要数工厂里的打字员等,他们的工作要么已经被电脑取代,要么都外包给了更贫困国家的工人,因为那里的人工成本更低。不过,在收入处于底层的许多行业中,也有一些工作所提供的收入和吸纳的就业人数出现了提高或增加。零售餐饮服务以及医疗服务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工作需要人际交往而无须高水平的认知技能,并且难以被电脑取代。依据传统,女性是这类工作的主力军,但这又的确进一步增加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那些在其他领域表现出色的富裕阶层也需要得到服务,其需求从餐厅服务员、托儿所保育员、家庭保姆、月嫂、遛狗工、清洁工、购物助手到私人厨师、私人司机、私人飞机机长等,多种多样。在古代欧洲的贵族制度下,大庄园主通常都雇有大量的随从侍者,从某种角度看,如今富人阶层所引发的服务需求便与此类似,只不过如今的“唐顿庄园”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美国的汉普顿或者棕榈滩这样的新贵城镇。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服务群体收入仍然处在分配最底层,使得收入最顶层人群和最底层人群无论在收入还是工种上都越来越分化,而中间阶层,越来越空心化。
政治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也有影响。美国国会负责设定全国最低工资水平,在2013年,这一数字为时薪7.25美元或年薪14 500美元(一年按2 000小时计)。部分州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水平线,其中18个州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联邦政府设定的标准。不过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联邦政府的最低收入标准并不是根据通胀与市场工资水平的增长而自动调整的,所以,尽管国会不时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劳动者实际的工资收入值还是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当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收入增长时,最低工资与平均收入之比下降得更快。
每次国家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都会引发争议,雇员和雇主各有其政治代表,也会因此陷入争吵。这样的情况导致最低工资标准经常多年得不到改变。1981年1月1日,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就已经是时薪3.35美元,但直到1990年4月1日,这一数字都没有变化。1997年9月1日至2007年7月24日的近10年间,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维持在时薪5.15美元。如今的7.2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是从2009年7月24日开始实行的。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经常无法赶上通胀的速度。1975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时薪2.1美元,其购买力要比如今的最低工资高出1/3。也就是说,在1975年,工资收入最低者一年可以赚到4 200美元,正好达到一个美国三口之家的官方贫困线;而在2010年,最低工资收入者一年可赚得14 500美元,但这已经低于17 374美元的官方贫困线。最低工资标准长年被压低以及仅仅得到偶尔的不完全修正这一现实,也反映出低收入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步下滑。
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在政客和经济学家间一直饱受争议。过于简单化的所谓标准理论称,如果政府设置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劳动者的自由市场价值,雇主就会选择裁掉部分工资因此上涨的员工,因为这些人的贡献如今已经不及其所占用的成本。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与艾伦·克鲁格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证研究显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至少最低工资小幅增长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异端邪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不仅仅是那些利益直接受影响的人对此予以责难,就连很多经济学家也恼羞成怒。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这些与标准理论相悖的证据如果得到支持,就证明了“经济学里连起码的科学内容都没有”,“经济学家除了写些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之外,乏善可陈”。在结尾,他恭喜多数经济学家“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的确,经济学中没有哪项实证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存在政治利益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科学信用的自我标榜却更为普遍。这在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中暴露无遗,而且绝不仅限于争论双方的某一方。但即便如此,普林斯顿大学两位学者的实证研究中有一部分却是绝对毫无争议的:对于所有的就业人员而言,最低收入的降低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它使得一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低收入值出现了。这种效应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或者职业而言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低收入地区、低收入职业,或者妇女以及非裔美国人这样的相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影响深远。
如果真实最低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断下降是导致低收入劳动者真实收入总体下降的原因之一,那为什么相关部门或人士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去进行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工会组织尤其是私营部门工会组织的衰落是原因之一。1973年,24%的私营部门劳动者都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降低到6.6%。尽管20世纪70年代,公共部门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到1979年就停止了。如今,工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公共部门。而其他一些没有政治投票权的群体的出现加速了工会政治影响力的衰退。非法移民显然没有投票权,而那些合法进入但仍未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也同样没有投票权。1972~2002年,非美国公民占投票人口的比例上升了4倍,与此同时,相对总体人口,这些非美国公民也变得更为穷困。移民政策的变化使得合法移民的主流从相对富有的群体转变为相对贫困的群体,随着工会政治权力的衰退,他们发出的政治声音也越发难以为人所知。
另外一个重要的美国公民群体也同样被剥夺了投票权。在美国,只有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允许重犯在监狱投票,但是剥夺重犯投票权终身的州却有10个,即便是这些重犯服刑完毕假释出狱,投票权也无法恢复。1998年,人权观察集团估计有2%的美国投票适龄人口在当时或永久丧失了投票权,其中1/3为非裔美国男性,也就是说,有13%的美国非裔男性没有投票权。在亚拉巴马州,超过30%的非裔美国男性丧失了投票权,在密西西比州也大致如此。即使是在相对自由的州,比如不会剥夺犯人权利终身的新泽西州,也有18%的黑人男性没有投票权。如此多的人没有投票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与投票,这使得他们远离了政治生活,基本上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如此一来,政客们也就完全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的诉求。
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与他们的工作年限、储蓄水平、雇主对退休金的支付比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密切相关,这部分人不会立即感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过,这部分资金是政客们和各种政治权力角逐的另外一个战场。老年人虽然并非特别富有,但是人数众多(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龄,老年人口在持续增长),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投票,而他们的游说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则是华盛顿最有权势(也是最令人恐惧)的政治团体。
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保障情况的鲜明对比,显示出工会力量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影响力的上升。此外,老年群体还从美国政府为其提供的医疗保障项目——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将这一医疗保险制度上的支出也算作受益者收入的一部分,那么老年人的真实受益程度要比其单纯现金收入所显示的要多得多。尽管其他的政治游说团体,比如为医疗保障提供商、保险公司以及医药公司利益代言的说客们都在各展其能,但是老年人强大的影响力还是在发挥重大作用,足以维护其目前的各种既得利益。
税收是政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累进所得税制使得富人虽然也有税收抵免,但交的税总要比穷人多,通过这样的设计,不同收入阶层的税后收入分配自然看起来比税前的要公平了许多。不过,累进制受到了持续的批评和质疑,比如大家一直在讨论,资本利得和股息收益是否也应该算作其他收入?此外,左派认为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来实现公平,而右派则认为每个人只要按其收入比例纳税就万事大吉了。
大约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无须支付联邦所得税,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后,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上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因为贫富差距主要是由税前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80年代,政府推行利于富裕群体的减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在90年代,政府对顶层收入群体增税,同时扩大了对劳动收入所得税的减免,使得最底层收入群体真正受益。不过,2000年以后,减税的政策再一次让高收入人群获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称,1979~2007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测算,但做了微小的测算方式调整)比例在税前增加了25%,而在税后增加了30%(将老年人医疗保障计划计算在内)。税前税后如此大的差异,部分原因就在于在整个时间段内累进税制的执行效果不足。此外,用于收入分配调节的转移支付也存在问题,老年群体因影响力强大而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而政治影响力微弱的贫困人群却未能从这方面获得多少好处。
上班族会把工资拿回家供全家使用,也有一部分人将收入完全用于个人开支;还有一些家庭则完全没有工资收入,包括那些依靠私人资助或者政府养老金的退休人员。除去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情况,家庭如何构成、如何运行以及谁在赚钱养家等进一步促成了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的现状。而某些发展趋势,比如女性工资相对男性工资的增长、1985年以前黑人工资相对白人工资的增长等,的确抵消了部分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距的扩大。如果我们观察全体人口的工资收入,即不管他们是否就业也不管种族性别,则可以发现,相对于就业人口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而言,全体人口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张要慢得多。就业人口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扩大,然而,由于很多之前不工作也不赚钱的人口,特别是已婚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差距的影响也被部分地抵消了。像全职白人男性这样的群体,其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变大,然而伴随着女性工资收入相对男性收入的增长以及非裔美国人工资收入相对白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缩小。
相对于工资收入,其他方面的改变实际上对家庭收入的分化影响更大。如今,高学历的男性更倾向于寻找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作为伴侣。尽管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在50年前,高学历男性的妻子极少会和低收入男性的妻子一样频繁外出工作。这些女性尽管拥有高学历,然而多数会遵循当时的社会传统,主要做她们事业成功的丈夫的贤内助。今天,在婚配上,夫妻双方仍然在学历水平上追求门当户对,不过,以前或许仅仅是丈夫拥有高收入,而如今妻子自己也可能是高收入者。“最有权势夫妻”指的就是那些夫妻两人都有顶级收入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使得家庭收入的顶级水平大大超出了个人工资收入的顶级水平。要反证这个结论,一种办法就是将所有被调查的夫妻全部拆散(仅为统计意义上),然后随意重新搭配,组成新的夫妻,然后再计算家庭收入的分配状况。这样做当然不能消除家庭收入中存在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重新组合之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大降低了。
权势夫妻组合使得顶级家庭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无所依傍的情况则让底层人口的贫困程度有所加深,其中尤以单身母亲家庭为甚。单身母亲家庭的数量在近年来大大增加,并且已经超过了普通夫妻家庭的增长数量,与正常家庭相比,单身母亲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除此之外,家庭组成的变化也扩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有权势的政治团体不断对政策制定者施压,也促进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全球化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也极为重要。医疗保障支出的快速增长拖累了工资的增长速度。教育激励机制得到重视,忽视教育激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为那些放弃学校教育的个体,以及因为缺少能力与背景而没有接受教育机会的人群都因此受到伤害。如同在家庭中将房间的整洁程度与零用钱数量挂钩一般,激励机制也导致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最顶端和最底端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然而中间阶层却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工会参与人数下降,政治影响力衰落,劳动力中无投票权且生活贫苦的移民数量上升,非裔美国人无投票权或被剥夺投票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人口在政治影响力的竞赛中完全败下阵来。老年人在人数、选票影响力以及政治游说等方面的势力不断扩张,使得这一并不贫困的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分配。不过,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最成功的那部分人仍然是收入处在最顶端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正是我在下面要详细考察的。
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思两位经济学家在2003年的调查改变了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方式。在此之前,人们都知道对于了解顶端家庭的收入,家庭收入调查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家庭很少会经常性地出现在国家范围的大调查中,即便偶尔出现,也很可能不会对调查问卷做出回答。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思采用了一种新的调查方法:通过所得税记录来研究收入不平等现象。这种方法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使用。和所有人一样,富人也毫无例外地需要进行纳税申报,如此一来,他们的收入情况自然就可以从所得税数据中一览无余。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思得出的结果改变了人们思考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们对顶端家庭收入的理解。后续的研究则考察了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数据作为参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美国之外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在这一章中,我之所以要拖到现在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想给它以特别的关注,同时也是因为它本身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政治上的变化极其重要。我也相信,仅仅是考虑到这些家庭所占有的财富数量如此之大,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
图5–4是皮凯蒂和塞思论文中一张关键图的升级版。图中的数据是从美国开征所得税的年份即1913年开始,到2011年大衰退时结束。这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时期的数据,前者以浅阴影标明,后者则以深色阴影标明。图中三条线分别表示纳税额处于前1%、前0.5%,以及前0.1%的税收单位,表示他们的收入占个人收入总额的百分比。图右边的美元数字,表示每个群体在2011年时的平均收入水平:纳税额位于前1%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110万美元;纳税额处在前0.5%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170万美元;纳税额处在前0.1%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500万美元;纳税额位于前0.01%的税收单位(图中未显示),其平均收入为2 400万美元,占该年美国总收入的4.5%。如果将数字放宽,则纳税额处在前10%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25.5万美元,这一群体在2011的总收入约占当年美国总体收入的47%。(一个税收单位不等同于一个家庭,以税收目的计算的收入也和为其他目的计算的收入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大部分是重叠的,因此总体的结论并无误导。)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高收入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呈现U字形走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需要资金支持,税负多数落到了企业头上,导致富人所获得的股息出现了急剧下降,高收入者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也因此出现大幅下跌。此外,在大萧条时期,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也出现了急剧下滑。“二战”之后,这种下跌的趋势依然延续,但是跌势趋缓。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情况出现了逆转。1986年,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出现了急剧上扬,并在此后持续增长。到了2008年,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再次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1986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税制改革,对课税收入标准做了重新定义,这导致当年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变化剧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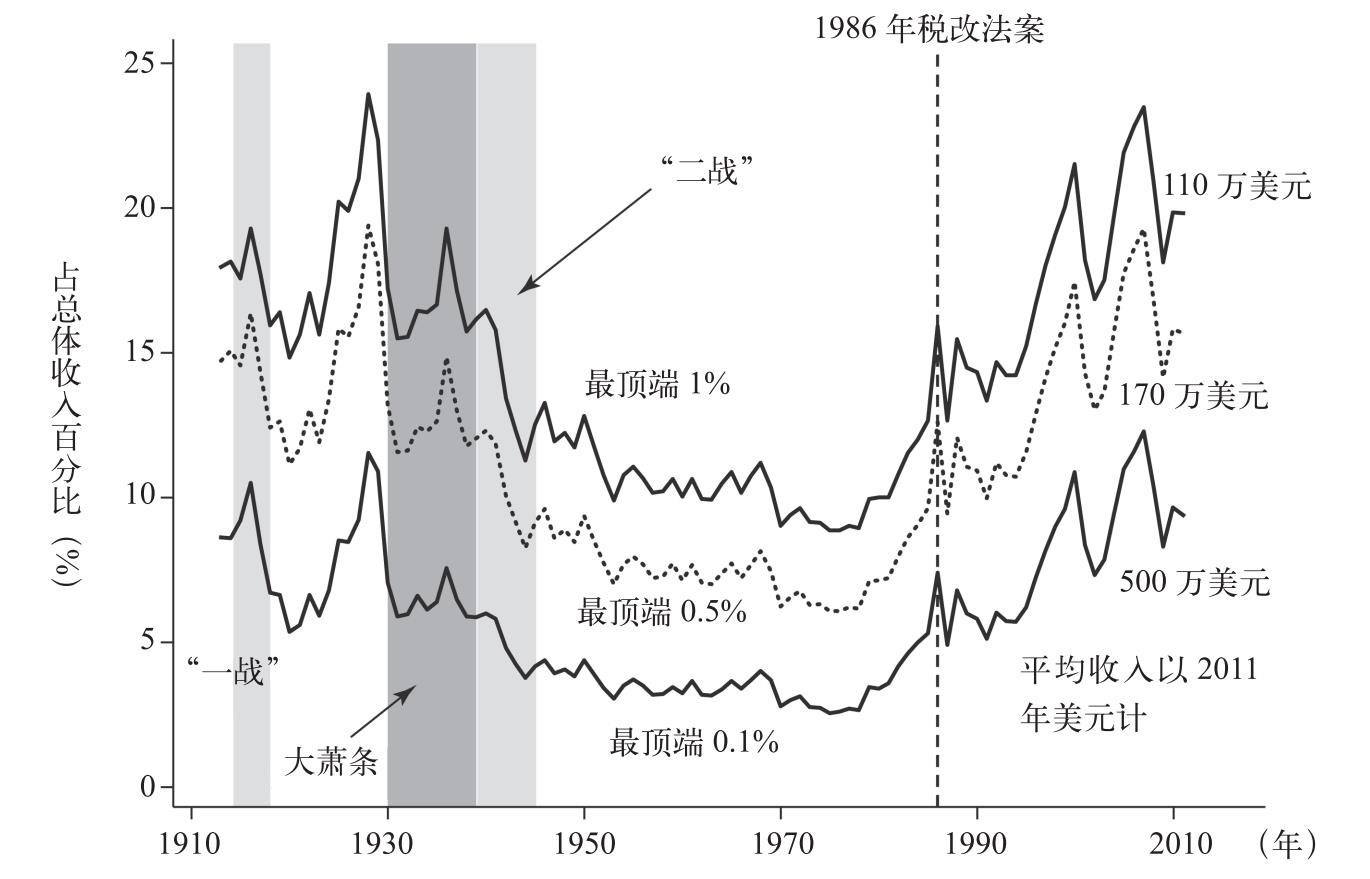
图5–4 顶级收入(含资本利得,1913~2011)
不但高收入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在变化,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也有变化。在早期,高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所得,因此最富有的那群人的收入主要来自股息和利息,正因如此,他们被皮凯蒂和塞思称作“靠剪息票为生的富人”。不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累进制收入所得税和房产税不断增加,人们以此获得的财富逐步减少,以前那些依靠自己或祖先的财产而生活的人逐步跌出最高收入的群体,而那些以薪酬作为收入的人,诸如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华尔街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等,依靠年薪、奖金以及股票期权等收入,成了新晋的高收入人群。企业经营所得在100年前是高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今仍然如此,其在高收入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与那些靠剪息票为生的富人,或者说是“有闲的富人”被“富忙族”所替代的重大变化相比,这种收入来源的稳定性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那些光芒耀眼的前0.1%群体来说,资本收益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工资收入如今已经是占比重最高的收入来源。纳税额处在前10%的群体,有近3/4的收入来自工资,而处在收入前0.1%的人,其工资所占比重为43%。而在1916年,这类精英阶层的收入中只有10%是来自工资。股息和利息收益仍然占总体收入很大的比重,不过,由于现在很多股票为养老基金所持有,因此它们的分配更为广泛。
过去的30年间,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最高收入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之间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纳税额处在后90% 的人群,其扣除通胀之后的税前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0.1%,在28年间的总增长率只有1.9%。这使得每一代新人几乎只能维持与其父辈相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税后标准看,并且算上每个人所占的养老保险支出份额,那么这后90%人群的生活水平改善情况会更好一些。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1979~2007年间,纳税额处在后80%的家庭,其税后收入增长了约1/4,年均增长不到1%。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但是这项制度的好处多数都为老年人所有,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钱并不能用来支付房租或者购买生存必需的食物。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处在前1%收入的纳税人,其税前收入增长了2.35倍;如果在1980年和2011年,某个纳税人的收入均处在这前1%的范围之中,那么其收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处在收入最顶端万分之一以内的群体,其收入增长则超过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是税前的,若是看税后收入,则从2001年起,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实施减税政策之后,高收入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还要更快。大众与少数富人之间这种财富增长速度的鲜明对比,可以很好地解释本章图5–1和图5–2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增长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同时,消除贫困的工作为何会如此失败?此外,这些鲜明的对比同时显示出,生活条件没有出现大幅改善的群体并非只有穷人。
富人变得更富,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因为富人像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一样,通过普惠大众的新型生产方式创造出了更多财富?如今的世界,人人都在努力奋斗,但一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为富有——那些对贫富分化的抱怨是正当的,还是仅仅出于嫉妒?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不平等?如果人人享有平等机会,付出更多便得到更多,那为何这样的事还需操心?而如果人们不能享有均等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担心的就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了。
我们常常被告知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并且被劝诫不要否定那些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成功的人。不过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梦就是人人可以成功,但实际上,美国人所获得的机会并非特别均等。衡量机会是否均等,上下两代人之间收入的关联度是一个常用指标。在一个完全流动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机会,你的收入和你父亲收入的高低不会有任何关系。而在一个阶级世袭的社会,工作岗位也是一代一代继承的,则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收入关联就是100%。在美国,这种收入的关联程度大概为50%。这样的关联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这种收入关联度高于美国。事实证明,只有在收入极为不平等的国家,父子两代的收入高低才密切关联;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收入不平等国家,其实也是机会极为不平等的国家。通常,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才是我们最想追求的,但实际上这两者经常同向而行,收入不平等常常也伴随着机会不平等。
那么是否存在对富人的嫉妒问题?经济学家钟情于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法则”,按照这个法则,如果一部分人在变得富有的同时其他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正在变得更好。所以,就不应该有嫉妒存在。有些人经常以这个法则来强调要关注贫困人口的问题,而不是去操心最富的人在做什么。用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话说:“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帕累托法则常常被视作真理,但是我们将看到,它并不能说明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近几年最顶端收入者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导致的后果。
与其他人群相比,顶级收入群体的内部分化其实并无不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科技发展使得那些学历更高、创造力更强的人获得了新机遇,而那些最有学识、最具创造力的人虽不能全部发财致富,但至少他们中那些最幸运的人都赢得了巨额财富。这其中就有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如今,娱乐巨星和伟大运动员的发展都不再受到地域限制,因此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也随着受关注度的扩张而增长。全球化使得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同娱乐明星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实现利润扩张。实际上,从整个世界来看,能够从自己的独特天赋中获益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多了。
另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富人群体是银行高管以及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接受了高等训练,并且利用受到的训练与自身创造性,生产出了很多新金融产品。不过,他们发明的这些新金融工具在产生大量利润的同时到底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对此经济学家也无法达成一致。有时候我们很难不同意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说法:ATM是最后一个真正有用处的金融创新。如果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个人目的而夸大了其社会动机,那么我们得到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可能已经超出所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他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就绝不能说是无可非议。
在贯穿经济始终的金融创新中,金融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金的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最有价值的任务之一,但是如今人们普遍质疑一些暴利的金融活动并未能让整体人群受益,反而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沃伦·巴菲特称这类产品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如果真是如此,通过这些产品所获得的高薪酬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而言,大量最优秀的头脑都集中到金融工程领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为它使得其他领域的创新和增长潜能受到了抑制。政府隐性担保行为的危害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有金融崩溃的风险,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丧失就业机会、收入下降或者陷入债务泥潭,政府也会对那些规模庞大且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施以援手,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是在鼓励过度的风险偏好。金融机构拿着自己或者客户的钱去逐利是一回事,政府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普通公众的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这样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危害,那么政府的做法就绝对不能容忍。
薪酬大幅增长的群体绝不限于金融企业以及一小部分超级创新者,实际上,很多美国公司高管的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有的人为这些高管辩护说,如今企业管理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企业的规模更庞大了,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高管们可以管控更多的人。但是很多人对这样的解释有所质疑。首先,图5–4中所显示的财富增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技术进步不足以对此做出全部解释。其次,不少西方经济体尽管也采用了新的管理技术,也同样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但是相比美国,其高管的薪酬增速非常缓慢,有的甚至就没有增长。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英语是全球通用的经济语言,因此英语国家的经理人在很多国家都会更受青睐,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全球化最受益的群体之一。实际情况似乎也的确如此,英语国家经理人的收入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一项研究指出,石油公司的高管薪酬会随着油价走高而增长。这说明,高管们并不是因为做出了什么成绩,而经常是因为公司的营收增长了,报酬也跟着水涨船高。当企业效益好的时候,高管们的薪酬就会增加,然而当企业效益下滑的时候,高管们的薪酬却没有相应减少。实际上,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多是些有名无实的独立董事,他们经常会为高管们制定出天价的薪资。正如巴菲特等人所指出的,这些独立董事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董事会所决定的,而且,这些独立董事也完全在CEO本人的操控之下。巴菲特同样提醒大家注意这些薪酬顾问所扮演的角色,他戏称这些人组成的是一个“薪酬高一点,再高一点,对了”的乐于助人型团体,其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让一家又一家公司采纳了巨额薪酬的政策而已。聘用这些乐于助人的独董,加之各个公司的CEO又经常在不同董事会交叉任职,最终使得整个金融行业以及其他企业都采纳了巨额薪酬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关于激进累进税制的共识与“二战”之后的平等化进程都在20世纪末遭到了破坏,相对于50年前,高管高薪酬现象变得更为普遍了。
政府的行为也推动了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做出“太大而不能倒”的承诺,并且让这些机构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无疑是监管失败的表现。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部门的薪资收入非常高,但是由于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监管趋于严格,这些部门的收入出现了下降。不过,在近年尤其是1980年以后,金融部门的薪资又开始上涨。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示,允许银行拥有多重分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利率上限的设置以及银行与保险的分业经营——这四个方面的监管以及去监管举措恰恰与收入的涨跌变化相关。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2年的施行以及1999年的取消,可谓是高薪资涨跌的两个重要分水岭。
国会批准或者废除法律的决定也并非全然不受左右。在国会之外,潜在的赢家和输家所进行的游说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些资金充沛的利益群体知道如何利用金钱来操控政治活动。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认为,政治游说在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发现,在华盛顿代表不同企业利益的注册说客,从1971年的175人增加到了1982年的2 500人。这一数量的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府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在商业监管方面的新政策。对于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而言,那些事关市场运行、公司经营权限以及会计准则的法律条文虽然看上去晦涩难懂,但它们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会引起牵涉数额巨大的利益变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取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无论在大衰退之前还是之后,这样的事例都有很多。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半公共性房地产抵押贷款金融公司房利美。负责运营这个公司的政客们长袖善舞,他们以雄厚资本展开游说,对政策制定施展政治影响。这个公司逃开了监管,政客们自己和该公司众高管大发其财,然而这也导致了其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的灾难性风险。
即便上述所说的只有部分正确,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会因为金钱政治而自我强化。所有的政治规则都是基于富人的利益而定,而非公众利益;富人们利用这些规则又变得更为富有更具政治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高收入者收入部分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恰恰是对高收入者减税最多的国家。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和马丁·吉伦斯对国会的投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国会两党都对富裕选民的意愿极为敏感,而对贫穷选民的诉求则非常迟钝。
大量人才流入为社会所诟病的金融工程领域对整个经济都有害,同样,人才大量流入游说行业也对经济发展不利。人们早就认识到游说行业是“不直接产出收益的逐利活动”,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它甚至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额的薪酬和相对低廉的成本,使得大量人才脱离了经济增长所倚仗的生产与创新行业而转投游说行业。如今,总统选举的支出已经比不过汽车厂商一年的广告预算,然而政府的支出以及不断攀升的选举成本仍是一个被频繁议论的话题。毕竟,相对于潜在的收益,政治上的金钱投入简直不值一提。
有一次,我坐飞机从德里前往拉贾斯坦邦的斋普尔,身旁坐了一位制造商(我一直没搞清他是生产什么,只知道那是一种享受进口保护的产品)。这位老板向我详尽地描述了政府监管者的种种作恶行为,并告诉我他在申请许可证和获取监管宽容,以及获得有利解释规则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包括这趟旅行也是为了这类事情而进行。他对这些监管者的厌恶蔑视情绪简直如洪水泄闸。在五星级的斋普尔皇宫酒店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他告别我前去会见那些他所鄙视的官僚,一边起身还一边小声对我说:“啊哈,迪顿教授,一切都是为了利润,利润啊!”我估计除了他之外,那位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撤销才创建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吧。
尽管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对于金钱与政治是如何互为因果这个问题都开始表现出强烈兴趣,这个问题还是未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现在所困扰的是无法对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做出很好的分析。高收入中哪些部分是来自游说或者其他的政治活动,哪些是因为高收入群体本身的能力?有多少政治活动是这一利益群体针对其他群体,比如工会这种也在华盛顿拥有说客的利益群体所开展的?这些影响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得更有力量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关键,因为它们将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担心高收入者收入的增长,以及证明为什么说关注富人变得更富绝不仅仅只是出于嫉妒。
如果民主政治变成了富豪统治,那就意味着非富有人群的权利实际上遭到了剥夺。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美国要么就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两者不可能兼得。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政治平等,而政治平等总是处于经济不平等的威胁之下。经济越不平等,则民主政治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如果民主遭到损害,则人们的福利就会遭受直接的损失。因为人总是会理性地判断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一旦这种能力受损,则其他方面的利益也有受到损失的危险。最富有的人对国家提供的教育以及医疗并无多少需求,因此他们会竭力支持减少老年人医疗保险基金,并与任何增税的行为做斗争。他们不会支持人人享有医疗保障,也不会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忧心。他们会反对任何针对银行追逐利润的限制性监管,而绝不会考虑这样的监管会帮助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能保护公众远离掠夺性贷款和欺诈广告以及预防金融危机的重演。对极端不平等后果的担忧绝非是出于对富人的嫉妒,而只是害怕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损害。
帕累托法则并无过错,只要一些人的财富增长不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伤害,我们就不应该盯着这些人的财富。现在的错误在于,许多人仅仅是将这个法则用于衡量金钱多少,而金钱只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方面,人类幸福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比如,拥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拥有健康,不能变成他人发财致富的牺牲品等。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即便没有影响其他人群的收入,但只要损害了其他方面的福利,那么帕累托法则就不能成为为高收入者辩护的说辞。金钱和幸福绝不等同!
如果我们只将目光聚焦于收入问题,而不考虑收入不平等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伤害,那么对收入不平等是否公正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看这些高收入者是做了造福大众的事,还是自己独占利润。乔布斯去世后举世哀恸,如果这个国家的某个大银行家也英年早逝,是绝对不会受到如此待遇的。
今日的美国就是阐述本书主题的一个极好样板。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持续增长,其速度虽然不是史上最快,但即使是以历史最高标准来看,这种增长也是值得赞叹的。经济扩张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这当然不是一个脱离贫困与匮乏的过程,因为美国在1945年就已经相当富裕了。但即便如此,经济增长对于大众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人们的居住条件变得更加安全优越;出行非常便捷,为先前所不能及;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讯以及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在以前,这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在通信方面,如今人们的交流方式更是前人所不能想象。当然,和以往一样,经济增长也造成了分化,一些人做得比其他人更好,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开始变慢,更缺少包容性。这种分化时常是有益的,因为它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对落后者产生了激励,物质收益也因此从惠及少数人逐步变为惠及更多人。在历史近期的美国,这体现在教育与科技的相互竞争中,受教育的美国人数量因此有了大幅增长。
发展与不平等之下落后者的追赶是光明的一面。不那么光明的是,落后者的追赶实际上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至今也没能真正追赶上来。在历史的长河中,1750年之后,西方迅速发展,而东方和南方却为什么没能做到?历史学家埃里克·琼斯对此有精彩的解释。他认为并非其他的世界没有出现发展,只不过是其他世界的发展总不能持续,而且经常出现倒退。在那些地方,一旦发展开始萌芽,掌权的统治者或者教会人士要么将其据为己有,要么直接将创新活动消灭,因为这些活动影响到了他们的地位。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持续的发展一直不能够实现,而那些本可以“下金蛋的鹅”也在刚降生之初就遭到扼杀。在这些社会中,权力的极端不平等致使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一条走出贫困脱离病苦的道路也就此被切断。
关于不平等对发展的阻碍,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与肯尼斯·索科洛夫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在那些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国家,比如在种植园经济中,例如拉美或者相对于美国北部而言的美国南部,富人都会反对大众的解放,同时将受教育的权利限制在他们自己所属的精英群体中。这样就使得大众得不到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也就无法为广泛的经济增长创造出相应的机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较早地开展了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教育,而这正是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护精英利益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害,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以及哈佛政治学者詹姆斯·罗宾逊的观点。那些为本国侨民创建聚居点的殖民主义者会将他们的制度也带到殖民地去(参考一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的历史),而在那些难以定居的地方(比如疾病横行的地方),殖民者往往会建立起以资源掠夺为核心的榨取型政权(比如玻利维亚、印度或者赞比亚)。在这里所存在的制度体系主要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而不会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榨取型政权通常无心保护私有财产,也不会推进法治,而没有对财产的保护和法治体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也难以兴旺。在殖民时代,相对富裕的国家或者人口众多的地区,往往是征服者的目标。如此一来,财富就出现了历史性逆转。在所有被欧洲强权所征服的地方,那些原本富庶的国家现在都变成了贫穷国家,而那些原本穷困的国家现在倒变成了富裕国家。
这种财富的大逆转足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繁荣与经济增长并非是理所应当的,不是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寻租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每个群体为日渐减少的总体财富展开更为凶残的争夺,而这种两败俱伤的战斗最终会让经济发展终结。利益集团会以牺牲大众权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私利,而对于大众而言,由于每个人的权益只是损失一点点,因此他们并不会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众多这样的集团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会从内部将经济掏空并且扼杀经济增长。掌握权势与财富的精英群体以前就做过杀鸡取卵的事情,而一旦经济广泛增长所需要的制度体系遭到破坏,他们也会趁机再次做出扼杀经济增长的举动。
“二 战”之后,现代国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很多国家,经济增长使得亿万人民逃离了贫困。死亡率下降,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的寿命延长,生活也变得更为富足。但一如既往的是,各个国家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这也使得它们和那些更落后的国家之间距离更远。亚洲那些曾经穷困的国家如今都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许多非洲国家与它们之间的差距因此而拉大。
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使世界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一场真正的“人口爆炸”也因此出现。在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世界贫困人口却在减少,这令不少当年的评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声称日益逼近的人口爆炸会让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伟大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就曾经抱怨说,在20世纪有三大灾难:一是内燃机,二是人口爆炸,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那个时代,多数人认为人口爆炸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尽管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又增加了40亿,地球上这70亿人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
不过,对于那些相对更贫困的人口而言,平均值给不了他们任何安慰。从美国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未被平等地享有。美国并不是一个孤例,很多国家都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化情况。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否也是如此?这几十年来,许多当年落后的国家都抓住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了那些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知识与技术,从而节省了不少时间,少走了弯路。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内地与印度都因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并非每个国家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多50年前很贫穷的国家如今仍然无法追上中国内地、印度或者亚洲“四小龙”。
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并没有缩小多少。一个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同时,另外一个国家也就因此更加落后,在今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和以前一样大。如果我们以平均收入为标准对所有国家按最穷到最富进行排名,然后将相对贫穷的国家(比最贫困国家水平高1/4的国家)与相对富裕的国家(比最富裕国家水平低1/4的国家)进行对比,会发现,1960年,相对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约为相对贫穷国家的7倍,而到了2009年,它们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扩大到了8.5倍。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这段时间里,人类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发展成就,堪称人类发展的奇迹。这段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它如何消灭了旧的不平等却又制造出新的不平等?这些是我们在本章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将深入讨论相关数据,并辨别其真实性。要对全球的贫困以及不平等做出全面评估,要面对诸多困难。首先,在很多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另外,面对那些随波逐流的观点与说法,我们本应有更多的思考,而实际上却未能如此。
要对物质生活水平进行评估并非易事,即使“收入”这个日常用词其实也非常难以确切定义。除此之外,贫困、不平等这些方面的评估标准,也未必比收入的评估标准更清楚;在进行跨国比较时这种困难会更为显著。怎样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免于贫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居住的人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国家贫困线也无法确切反映在某个具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成本,况且,不同的群体对于需求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多数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贫困线视为一个判断能否生存下去的合理数字。但如果我们要对全世界范围的贫困进行评估,就需要确立一条在全世界范围都合理的贫困线——既适合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适合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马里的廷巴克图。当然,它也需要适合发达国家的城市,譬如英国的伦敦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要做到这一点,以便对全世界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需要能够对不同的货币价值进行等价换算。也许我们会将等价换算的实现寄托于汇率,不过,汇率本身对此无能为力。
一种货币如何才能等价转换为另外一种,比如美元如何才能变成印度卢比?这里存在一种每天都会变化的叫作汇率的东西,它表示在市场上1美元能够兑换到的卢比。比如在2013年4月,美元兑卢比的汇率是1∶54.33。这意味着,如果我从纽约飞到德里然后在银行柜台前进行兑换,将可以用1美元换得大概50卢比。当然,因为银行需要从中赢利,所以我换得的卢比可能比这个数字少。但是,当离开机场进入城区,我发现,即使是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我用50卢比能买到的东西也比在纽约用1美元所能买到的多得多;而如果是在德里经济学院的食堂,或者是在当地街头,50卢比能买到的食物和1美元能在纽约买到的食物相比简直是丰盛到叫人无法相信。
简单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印度的物价水平要比纽约的低很多,如果将货币按照市场汇率进行换算,那么同美国相比,印度的大多数东西都会很便宜。事实上,根据最新的估算,印度的物价水平大概只有美国的40%。换句话说,如果美元兑卢比的汇率为1∶20,而不是现在的1∶50,印度和美国的物价水平才是相当的。这种让1美元在两地价值相当的“正确”的汇率,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汇率)。购买力平价汇率是以两地的相同购买力为基础换算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如果印度德里的价格水平比美国纽约的低,则购买力平价汇率会比外汇市场汇率低。多数贫穷国家的物价水平都比美国的低,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平价汇率都具有这种特征。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怎么算出来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基准的市场,所以,计算这样的汇率只能靠统计与发掘。相关研究和统计人员从全球各地收集到数以百万计的物品价格,然后计算出每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最早进行此类统计的机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欧文·克拉维斯、罗伯特·萨默斯和艾伦·赫斯顿首先对6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进行了计算。多年来,艾伦·赫斯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本书中的很多数据都来自他那里。这些创新者改变了经济学家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对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
在这种跨国研究对比中,我们首先会发现,印度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普遍存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物价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国家越贫穷,物价水平也相应越低。很多人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思议:一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会比其他地方的低,这怎么可能?如果德里的钢铁或者汽油价格都比纽约的低,那为什么贸易商不去德里买进这些东西然后运到纽约出售?实际情况是,如果将运输成本、税费和补贴考虑进去,钢铁和汽油等物品在纽约和德里的价格差距其实并不太大;但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如此。比如,德里的理发价格、曼谷的食物价格,放在纽约看绝对非常便宜,但是贸易商对这样的商品或服务却毫无兴趣,这其中是何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服务只在德里或者曼谷提供而不能搬到纽约去。贫穷国家的人民相对穷困,所以这些国家的服务价格也相对便宜,但是,多数价格低廉的服务是无法转移的。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将会下降,穷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如此一来,整个世界也会变得更为平等。不过,富裕国家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工资水平下降,因此他们反对人口的自由迁徙;而没有自由迁徙,上述结果就不会出现,穷国的工资水平就会继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于是那里的服务,比如理发和饮食的价格也就持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也同样无法在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对比。印度或者非洲的住房价格便宜,可是那里的土地不可能搬到美国按照美国的价格进行销售。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的存在,是穷国物价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市场运用汇率手段使得钢铁、汽油、汽车与电脑的价格在各国基本一致,因为这些产品都能够成为且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但是,一般而言,决定平均价格水平的是那些无法交易的物品和服务,而这类物品和服务往往在穷国相对便宜,所以,国家越穷,其平均物价水平越低。
正因为穷国的物价水平更低,如果我们使用市场汇率来比较各国的生活成本,就会导致结果的谬误。新闻报道经常犯这种错误,而经济学家也时常会落入汇率的陷阱。2011年春,印度政府在印度最高法院(既不明智又显悭吝地)宣称,印度人,至少是印度的非城市人口,每天只需要26个卢比就能够摆脱贫困。这一说法随即被媒体大肆炒作,印度以及国际媒体都报道称,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1.25美元,按照美元兑卢比1∶53的汇率,世行这个标准比政府所定的标准要高出两倍还多!不过,要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1美元约合20印度卢比,那么世界银行的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也就是大概25卢比——就和政府所建议的差不多。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金融时报》,也使用了市场汇率来计算美元与卢比比值,声称印度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实际上只有0.52美元一天,大大低于世行所制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印度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更为真实的数值其实是1.3美元,这虽然依然很低,但比起0.52美元这样的错误说法,这个数字已经翻了接近3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年来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一直备受人为夸大贫穷国家人口贫困状况的指摘。当我们谈及贫穷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时,只要使用市场汇率,则不论是工资水平、看病费用抑或是交通与食物支出,都会被低估1/3~1/2。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当然较低,这正是穷国的一个特质,但是过分夸大它们相对于富裕国家的贫困水平却没有任何益处。
当我们对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或者是统计全球的贫困状况与不平等状况时,购买力平价汇率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在这里,“跨国”这个词意义重大。当我们计算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时,会认为不调整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正确的选择。以美国为例,在堪萨斯或者是密西西比生活的成本当然要比在纽约低,但是别忘了纽约的生活成本虽高,同其他地方相比它提供的便利也多。实际上,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那么大城市的高物价水平就意味着这里提供了更多物有所值的便利。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对比跨地域的收入差异时就无须做出价格调整;纽约市曼哈顿区的高收入人群绝对比堪萨斯州曼哈顿市的低收入人群生活得更好。但是跨国的对比,比如要比较印度和美国或者法国和塞内加尔,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即便与在印度生活相比,在美国生活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对于这一点我有所怀疑),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和印度的物价差距是生活质量差距的真实反映。所以,当我们对印度和美国的收入进行对比并以此来评估国家间的差距时,就必须引入购买力平价汇率对物价进行调整。
进行跨国对比时,购买力平价汇率要优于市场汇率,但购买力平价汇率也远非完美无缺。对于不同国家的可比较项目,我们可以在各国收集其价格信息,然后进行计算。比如,我们可以收集计算河内、伦敦或者圣保罗地区1公斤大米的价格或者理一次头发的价格。但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对比定价。比如,一个贫穷家庭在农村的自建房屋应该定价多少?在城市贫民窟搭建的一顶帐篷又该如何定价?富裕国家存在着多层次的房地产租赁市场,然而在贫穷国家,这样的租赁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定价极为困难。在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等由政府提供的国民服务都非常难以定价,而要对这样的服务进行跨国对比就更是难上加难。国民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对于这样的项目我们只能靠估算——这虽然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但是其结果也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回归通常的汇率计算方式,毕竟我们已经知道那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要清楚,虽然购买力平价汇率更为准确,但是它也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存在。
对不同国家可对比项目的价格统计,还有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地方。以男士衬衫的价格为例,在美国,一个标准的统计项目或许是一个知名厂商生产的衬衫,比如一件布克兄弟(美国经典男装品牌)的牛津棉布衬衣。拿着这件衬衣与玻利维亚、民主刚果或者菲律宾等国家生产的男士衬衣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自己最终将陷入两种都无法令人满意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一件标准衬衣的价格一般都会很便宜,但是质量也要比布克兄弟的差不少。因此,如果将两者进行对比,实际上并不是在对比两种同样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会低估穷国的物品相对于富国的价格。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在这些国家费尽全力找出和布克兄弟类似质量的衬衣再进行价格对比。这样的衬衣,或许只在这些国家首都最好的商场里有售。但是这样的对比又会有相反方向的风险:我们能够在这些国家找到这样的衬衣,然而,这样的衬衣只在这些国家最贵最高档的商店中出售,且只有为数不多的权势人口才穿。这样,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高估了这些国家的物价水平。如此,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开始进行拔河比赛:是只统计国与国之间可对比项目的价格呢,还是只统计人们购买的有代表性的商品价格?极端情况下,如果在一个国家意义重大且使用广泛的商品,在另外一国全然不存在,那么这种对比就会失效。比如,画眉草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作物非常鲜见;豆腐是印尼人的日常食品,但印度人就很少吃;因为宗教因素,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没有酒类产品出售。
即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获得,不同国家的人对不同的商品也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也不尽相同。我在英国长大,如今却住在英国之外。这里就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在英国,有一种几乎可以归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叫作马麦酱。这是一种非常咸的酵母萃取物,是酿酒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最早由路易斯·巴斯德发现,随后被授权给一家英国的啤酒生产商生产。在英国,马麦酱价格便宜且消费量很大,卖的时候都装在大黑罐里;但是在美国,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虽然马麦酱也能买到,但价格变得很昂贵,而且包装也换成了小的。马麦酱是一种定义明确并且可以进行精确对比的商品,在英美两国,它的价格也很容易统计,但是,英国人对马麦酱的消费量要比美国人多很多。所以,若是以英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计算对比英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就会发现美国的价格水平要比英国的高;反过来,美国人热衷的全麦饼干和波本威士忌在英国没什么销量,价格也相对要高,若是以美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对比两国物价,那就会得出英国物价水平高于美国的结论。
英美这类富裕国家之间差距较小,所以无论是使用美国的商品进行比较,还是使用英国的商品做比较,其结果都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马麦酱这个例子说明了进行跨国物价比较的一个基本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消费更多在其国内相对便宜的商品,而对那些相对昂贵的商品消费较少。因此,如果用国内“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为基准来评价国外的消费水平,就难免有高估国外生活成本的风险。如果我们以国外的“一篮子”商品价格为基准,则又可能低估了国内的相对成本。在实践中,统计人员往往折中,以求出一个平均值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折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将英国的物价水平同西非国家喀麦隆的进行对比时,这一点就清晰可见。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在喀麦隆乘飞机旅行非常昂贵,因此使用航空旅行服务的人很少。但在英国坐飞机就很便宜,即便是相对不怎么富裕的人也可以乘飞机到国外度假。以喀麦隆的航空价格来衡量英国的价格水平,就会显得喀麦隆的物价极高。折中一下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无论如何,航空价格水平还是对喀麦隆的购买力平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喀麦隆的航空服务近乎为零,但如果将航空价格考虑在内,则喀麦隆的物价水平还是会高出2%~3%。在包括贫困评估等在内的一系列情境中,跨国物价的对比常常要依赖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这真是极为荒谬的。在这里,英国和喀麦隆的问题就在于两个国家的差别太大了,而英国和美国之间就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不过,与中美之间的物价水平差距相比,英国和喀麦隆之间的差别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依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测算,2011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 455美元,美国的则是48 112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的9倍。但是,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没有考虑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美国的2/3这个现实。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个更好的指标,我们将会发现,美国人的收入只有中国人的5.7倍,而不是8.8倍。对于军人或外交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多是依靠其资源总量,因此他们更关心这两个国家的绝对经济总量。而要计算这一数值,就需要根据中国人口与美国人口的数量比例将中国的数值乘以4.31。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经济总量的3/4。考虑到中国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且会保持这种趋势,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能一直保持比美国的高5个百分点,那么中国超过美国只需要6年。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对于数据的使用建立在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市场汇率一样可获得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知道,马麦酱的问题、喀麦隆的航空旅行问题,以及对典型的可对比项目进行类比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购买力平价数据,真实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可能会比我们的数据更高或者更低。在与艾伦·赫斯顿展开合作研究时,我们发现,如果将类似马麦酱的问题考虑在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考虑用中国或者美国的“一篮子”商品来对价格数据进行平均,则计算所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将会有大约25%的误差。所以我们只能说,2011年,按照国际元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3%~22%,而在总量方面,中国是美国的56%~94%。当然,这样的数据范围太大,如果做一些折中处理,得到的结果将更便于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折中毕竟是针对那些没有完美解决方式的概念性问题的一种比较武断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例子中,还有其他问题影响着最终结论的准确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那个长期存在并仍未尘埃落定的争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其数据是否可信?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猜疑。那么,如果数据真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调整?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一种跨国对比难以展开的印象,也不想让结果总是存在太大的误差。1949年,我当时的导师——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斯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对美国和中国或印度等国家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呢?这里面有何可能的利益关切?谁都知道从经济层面看,一个国家非常富裕另一个国家非常贫穷,但它们之间具体的差距是30倍40倍还是其他,这样的事情重要吗?”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大高于1949年时的情形,不用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就是大众媒体也一直在关注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超越了美国。此外,同我老师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在数据收集以及思考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想知道,富国和穷国之间到底差距多大。当然,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当我们将富裕国家和中国、印度或者更为贫穷的非洲国家进行对比时,这一点更为明显。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类似,相互对比时不确定性相对较少,因此下结论时较有把握。比如对于加拿大、美国或者西欧国家而言,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汇率的差别就比较小,因此在对这些国家进行对比时,我们的立论基础就比较牢固。
“二战”使得很多欧洲国家陷入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但在战争结束后,较为富强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战争的创伤被抚平,新的更高水平的繁荣出现了。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富裕国之间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越来越相近,和富裕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相比,富裕国家之间的相互差距已经变得非常小。图6–1显示的是24个富裕国家的国民收入变化(经过物价调整)情况。尽管目前关于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远非完美,这些富裕国家的数据却相对可信,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也较为可靠。和第四章的图4–4一样,图6–1也是一个箱形图,其中,箱体顶部和底部到线须部分,分别表示的是收入水平位于顶端1/4和底端1/4的国家,而中间的箱体,代表剩下的一半国家;箱体中间的横线,表示收入中位数。线须长短表示的是数据的离散程度,而另外一些箱形图之外的小点,表示极端个例。
图6–1显示,同美国一样,世界其他地区的富裕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的“战后黄金10年”,这些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速超过了4%,这意味着只需要10年时间这些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就可以增长5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下滑至2.5%;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数字又下降至2.2%;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一数字则只剩下不到1%。图中各国经济增速下滑如此明显,原因在于这一数据的统计始自战后你追我赶的经济快速增长期,而以这几年的金融危机作为结束。从废墟和混乱中走向复苏,虽然也非常艰辛,但和创造前所未有的收入水平相比,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人们知道如何从头再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需要重操旧技,而无须从无到有地创新。不过,一旦重建完成,新的增长就需要依赖新的生产方式,而开垦处女地比翻一遍旧沟渠要复杂得多。当然,在一个相互联系密切的世界,创新会很快从一个国家传播至另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国情相似的,因此,发明创造的重担也就由多个国家来共同承担。这样的密切联系本身就有利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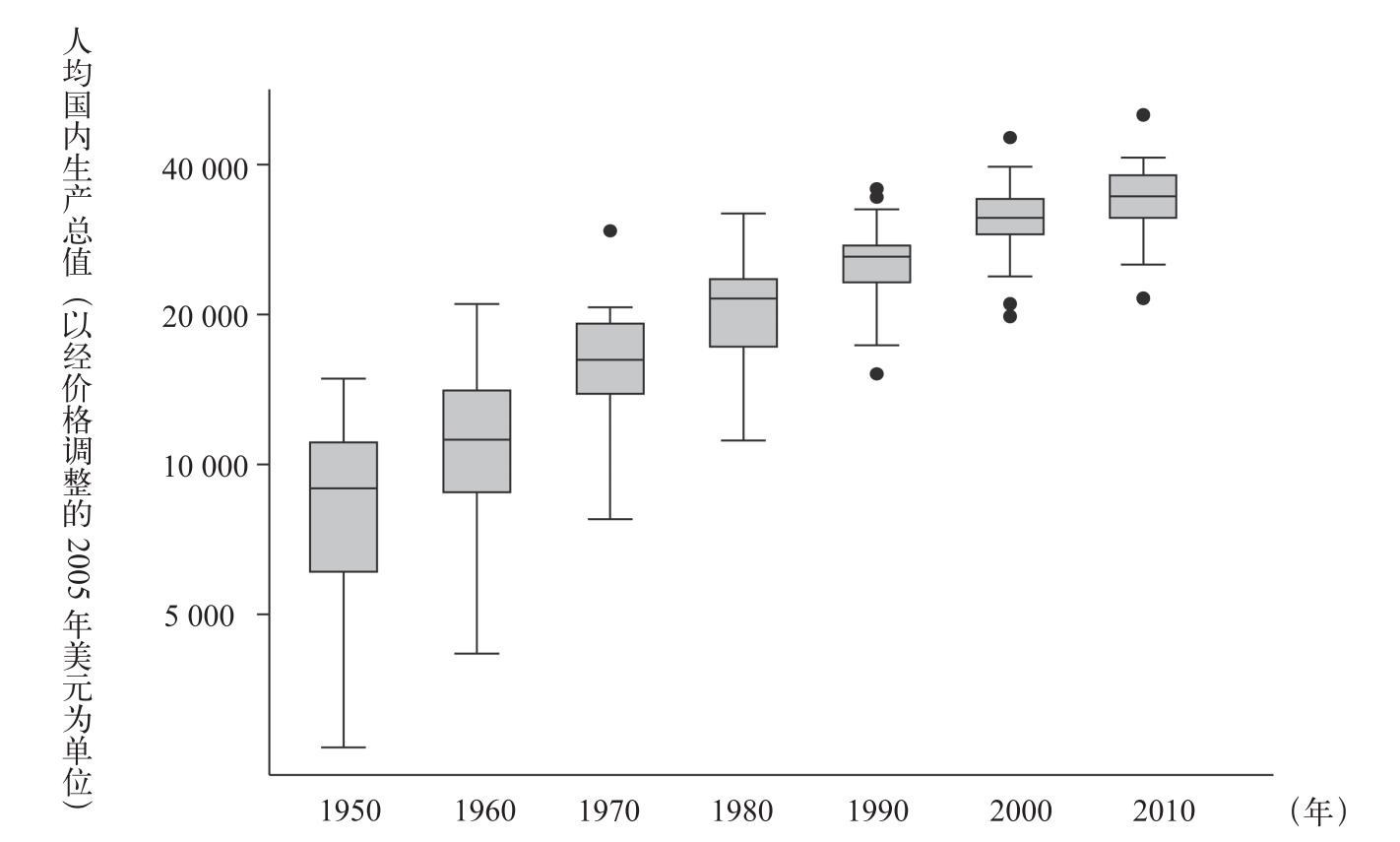
图6–1 24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注:24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
全球化使商品和信息的转移成本大大降低,商品和服务都得以在成本最低与效率最高的地区生产或完成;某个地区的新发现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各地采用。吸烟有害健康这种认知,或者降胆固醇药和降压药等新医疗手段,都会在极短时间内国际化,从而使得富裕国家的人口在健康和收入水平上越来越接近。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尽管进度各有快慢,但是良好的政治制度、医疗制度以及经济体系都会保证新技术得到应用,于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出现了一次显著缩小的过程。尽管近年来各国物质进步的步伐已然放慢,但新技术在实现了缩小健康差距的作用之后,仍旧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但是,国与国之间平均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内部的具体情况。从美国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平均收入的增长其实并没有被广泛享有,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并不能说明富裕世界所有公民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比如有两个群体,原本是分离的,但如今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群体内部的成员都各自分化,那么这种内部的整体差距就会抵消甚至大于两个部分合并所引发的差距缩小效应。从整体上看,如果我们忽略国家之间的差别,将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呈增长趋势。后面我讨论全球整体的不平等时会再涉及这一话题。
对于我们而言,或者至少是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出生在1945年之后的人们而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而国与国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世界。我们会认为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是理所应当的,经济也会持续增长下去,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健康差距缩小,旅行变得更简单更便宜也更节省时间,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获得。
但事实上,除了富裕国家,其他地方全然不是如此。图6–2也是一张箱形图,但与图6–1不同的是,图6–2不仅仅包括富裕国家的收入数据,还包括了所有贫困国家的数据。如预想的那样,当我们将贫困国家的数据包含进来时,平均收入水平的分布范围变大、所有的箱体部分变大、线须部分和小点所分布的范围也进一步变大。同之前部分国家的数据相比,整个世界范围的数据可靠性要低一些,而衡量标准存在的误差,也会导致收入的分布范围比真实情况要宽。一个不太明显却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当观察全世界的平均收入分布时,我们发现,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没有随着时代前进而出现缓和。图中,20世纪50年代的箱体部分应该先忽略掉,因为当时很多国家没有相关数据,同时不少非常贫穷的国家被遗漏,造成这一时间段的箱体部分位置过高,长度也过短。1950年之后,每个年代的箱体部分长短也几乎没有变化,如果我们看下面部分的线须长度,会发现实际上收入分化扩大了,尤其对于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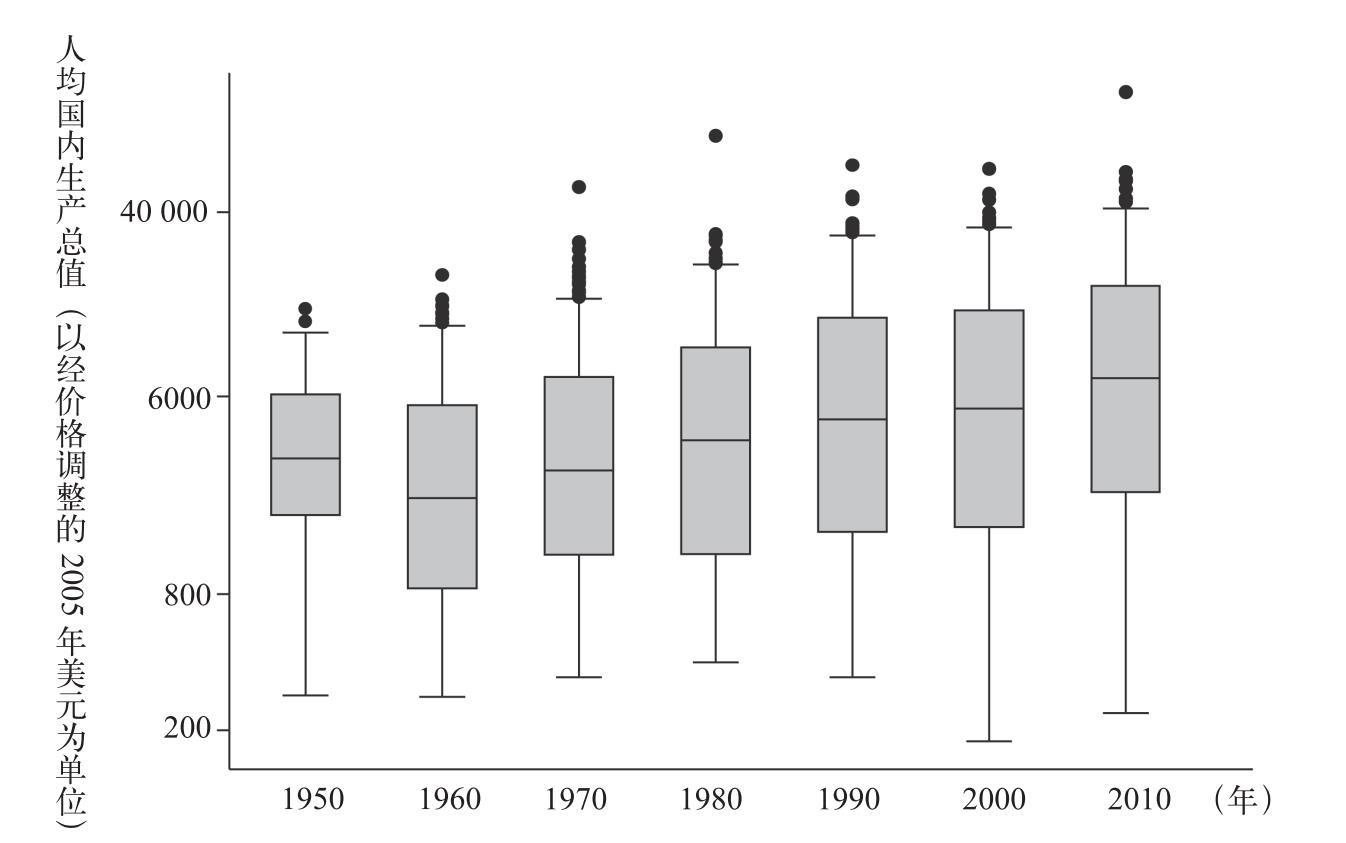
图6–2 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新的思想理念也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富裕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因此出现缩小。但是这一时期,一个更为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是:穷国的经济并没有借这个机会追赶上来,而这正是图6–2和图6–1看起来如此不同的原因。技术与知识是富裕国家实现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基础,而这些技术与知识也同样为许多贫困国家所获得。但是,占有同样的技术与知识却无法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获得同样的生活水准。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也必须具备与富裕国家同样的教育水平。但是,对于穷国而言,它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财力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会给穷国无穷的激励,让它们在基础设施与设备上加强投资。罗伯特·索洛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经典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平均物质生活水平肯定会趋向一致。但是,这样的情况为何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这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最好的解释或许是:穷国缺少相应的制度体系,比如它们缺少有作为的政府部门,缺少可执行的法律和税收体系,缺少对知识产权的保障,缺少相互信任的传统等;而这些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速并不比这些富裕国家低,有些时候甚至比它们高。但是,当一些国家快速发展、日渐追赶上来之时,总有另一些国家被进一步地甩在了后面。各个贫穷国家间的实际发展情况差别巨大,一些国家能够抓住机会迎头赶上:从1960年至2010年,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以及非洲的博茨瓦纳,都在以每年超过4%的速度增长。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平均收入增长超过了7倍。与此同时,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几内亚、海地、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以及尼日尔等国,在2010年时的情况比它们在50年前的还要糟糕。还有不少国家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找不到相关的数据(比如阿富汗、吉布提、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20世纪60年代属于东欧集团的几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本应不断缩小,但却又在其他方面出现较大失误,使得它们在缩小与他国收入差距方面以失败告终。
中国和新加坡是两个都在快速发展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300多倍。另外一个大国印度在发展速度上未能与中国比肩,但是自1990年以来,其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为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尽管中国和印度只是两个国家,但是它们在世纪末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世界上约40%的人口坐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与之相反,在经济增速出现倒退的很多国家中,出现了不少小国的身影(当然有很多例外,比如民主刚果人口很多,同时经济发展也极其失败)。
如果不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出现了高增长,而看有多少人口享受到了高增长,那么全球的经济增长形势将更为乐观。在1960年以后的50年中,全球国家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5%,但是全球个人的收入年增长率为3%。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它们的发展速度也比一般国家的要快许多。
要理解这一事实,不妨把全世界的人口想象成一支队伍,队伍里每个人都举着各自国家的旗帜,如同在参加规模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他们纷纷以各自所在国家的收入增速速率前进。结果我们发现,印度人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梯队走得非常快,而刚果人和海地人则在倒退。这时候我们观察整个群体,会发现其中2/5的旗子是中国和印度的,这一队人马一开始处在队伍最末的位置(在1960年时这两个国家都很穷),但他们稳步向前,虽然尚未到达最前方(他们离最前方的欧洲人和北美人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但也已经到了队伍中间的位置。当然,并不是这两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他们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印度人走在了另外一部分印度人的前面,一部分中国人走到了另外一部分中国人的前面。但是,现实是,这两个国家很高的平均增速,还是让亿万的人民脱离了贫困。虽然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整体差距没有出现任何缩小,但是由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快速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这就让整个队伍,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口看起来都一起向前了。
当谈到全世界人民的收入不平等差距是否缩小了这个比较宏大的议题时,我们经常因不确定性而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们当然可以给出更确切的回答,但这需要解决很多关键衡量标准不确定的问题,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速——有大量的专题文献试图解开中国国家统计那些令人费解的谜团。虽然多数作者都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被夸大了,但到底夸大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对于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我们也无法进行合理估算。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中国政府也没有参与任何相关的物价收集统计。如果世界不平等趋势的扩大或者缩小速度非常快且明显,那现有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倒是无关大局。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至少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可以跻身于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列。这是巧合,还是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所以发展迅速?其他的一些大国,诸如巴西、印尼、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在某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也会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却都不具备中印如此持久的增长动力。人口规模当然给“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带来了一些优势,毕竟人口众多,杰出的外交团队、有能力的官员、训练有素的领导层、一流大学所需要的教工队伍等都有人才储备。如果是一个人口极少的弹丸小国,这些发展所需的人才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此外,如果科学发现——或者对于穷国而言更确切的说法是,改造旧知识使之适应新环境——更多的是依赖科研人员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么,显然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更具优势。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曾经问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告诉他是全球贫困的衡量与评价。非常有趣的是,他又问我研究的是哪个国家,我回答说“印度”。这时他跟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如果是以科研人员的总量而非人均收入或者贫困人口的数字计算,这位物理学家是对的;而如果科研工作的溢出效应可以让每位国民都受益,那么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显然更具优势。但是,这种规模优势是否足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多的国家经济增速快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都是尚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
至于为何一些国家增长速度快一些国家增长速度慢,这里仍有很多未解的谜团。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增长一直快或一直慢的国家。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在这一个10年增长较快的国家,到下一个10年或者下下个10年,往往未能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日本曾经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永恒之地,但如今已风光不再。印度是现在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其国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低速水平,甚至出现过零增长的局面。中国是当前的长跑明星,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中国当前的增长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是极不寻常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的评论者都喜欢对几个高速增长的国家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会被列为“增长的秘诀”,只要未被证明失效,这些“秘诀”就会被一直大肆宣扬下去。同样,很多人也会盯住那些失败的典型(指收入处在最底层的那10亿人),然后总结出一些失败的特征来。这两种类型的努力,就像一个进赌场玩轮盘赌的人,刚上来就押注赔率极高的零号,除了掩盖我们根本上的无知之外毫无用处。
这些研究上的愚蠢,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苏格兰的一幕。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太了解经济增长情况,当然也不关心这种事,我们更多关心天气的变化。苏格兰通常寒冷潮湿多风,但在1955年和1959年,苏格兰夏季出现了长时间的温暖天气。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尽情在林间与水上玩耍,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是什么带来了那样的好日子?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有一阵子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小学,童年烂漫才是我感到欢乐的关键。但是大我几岁的表兄戴维却提醒说,当时他已经上中学了,也过得很开心,既然这样,那我所认定的小学关键论自然就是错误的。后来我又记起来,1955年和1959年恰好都是保守党在台上执政,所以或许欢乐时光之关键,不是小学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然,很明显我这样的推论是在胡扯,但那些基于巧合就想为某种成功或者失败做出愚蠢概括的人又何尝不是在胡扯呢。这跟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的占卜师用鸡的内脏来预测未来是一样的。
“二战”之后的60年间,世界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而人均预期寿命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详见第四章),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也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些发展奇迹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此前人们的普遍预测,甚至可以说是和人们的预测大相径庭。
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使得贫穷国家也获得了虫害防治技术、清洁水供应、疫苗接种以及抗生素,千百万人尤其是儿童因此得以幸存。儿童存活率的大幅提高带来了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穷国人民的生存机会渐渐追赶上了富裕国家人民,千百万原本会死去的儿童得以幸存。预期寿命的大幅增加人人乐见,但是它带来的全球千百万人口增长却并非人人欣喜。世界人口用了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才在19世纪初达到第一个10亿。1935年左右,全球人口达到20亿,也就是说仅仅用了大概12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增长了10亿。到1960年,即仅仅又过了25年,世界人口就增加至30亿。1960年世界人口的增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2%,而此后世界人口的增速并未出现下降,这样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世界人口在32年之后就可以翻倍。从这个角度看,人口正在爆炸性增长的说法并无任何夸大。
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发达国家的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学术机构、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开始对人口爆炸问题产生警惕。人们对此的关心多数是出于人道主义,毕竟很多穷国已经很难养活自己的国民,而更多人口的出现,肯定会让现实更加雪上加霜。这就好比一户贫困人家,省吃俭用才能够准备上一顿粗茶淡饭,结果发现还有一堆没饭吃的亲戚等在大门外。大规模的饥荒似乎近在眼前。在那些游览印度的游客看来,印度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当听说印度人口还会出现亿万数量级的增长时,他们惊骇无比。的确,对于那些第一次来到印度的西方游客,德里和加尔各答贫民窟里的穷苦潦倒和疾病蔓延,满街的乞丐、麻风病人以及伤残儿童,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人们,或者仅仅是如此密集的人群,就足以让他们震惊。如果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口出现,那这地方岂不是会更糟糕?
国家安全也是一个为人所担忧的问题。日益增长的贫困肯定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沃土,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出现,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其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还有一些大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也引发了部分人士的担忧。比如,优生理论一直十分关注人口的“质量”问题。尽管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优生学的概念已经不太流行且不受重视,但还是有人担心贫穷而且未受教化的人口可能比富有且受教化的人口增长得更快,从而威胁人类的未来。更极端的是还有人以肤色问题为借口,要求对非洲和亚洲的人口增长加以控制,为此,不少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国际组织也发放贷款,基金会更是提供援助,它们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让这些穷国少生点孩子,控制好人口规模。至于这些真正在生养孩子的贫穷国家是怎么想的,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为什么人口越多就越贫穷这样的思维如此普遍?有一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增加,那么人均所享有的食物和其他商品就一定会变少。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解释可谓是一种基于总量固定论的谬误: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某种事物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人口的简单算术增长会引发匮乏的发生——这就像一个穷苦家庭吃晚餐时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必然出现食物不够分配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带着食物来的,那么,这次聚餐很有可能无论是在营养还是社交方面都超出我们最初的设想。所以说,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对比。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多了一张嘴,但也多了一双手。这个解释虽然过于简单,但是与认定新增人口没有任何贡献的总量固定论相比,它还是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我们还需要看到,亚洲和非洲在人口爆炸性增长期间所出生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主动的选择。但在当年,即便是这样的说法有时候也会遭到质疑,亚非的人们被看作性欲的奴隶,而孩子就是这种欲望之下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后果。尽管在那个时候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如何方便而又低成本地避孕,但是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这个还需要证据的话),即便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如此,总体而言每个孩子的降生都是父母理性思考后的主动选择。所谓无限的欲望不过是我们西方人的一个借口,利用这个借口,我们对穷国进行所谓的“帮助”,让它们的人口减少生育。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而是我们不想要孩子。没有人能证明这些国家的人真的想要得到这样的帮助,也没有证据证明减少生育就能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有所帮助。事实上,一切恰恰相反。
父母想要多生孩子,并不必然意味着孩子越多这个社会越好;多生孩子的有些后果,父母也不清楚,而有的即使他们清楚,也可能会忽略。一个家庭的孩子增多,其他家庭的负担也会增加。当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都是由这个家庭自己负担时,我们相信,父母们会仔细衡量其成本和收益,而只有收益大过成本之时,他们才会做出生孩子的决定。孩子的出生或许会减少家庭中其他成员所享受到的资源,毕竟没有哪个孩子生来就能够为家庭经济做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为人父母的欢乐,完全可以说,多一个孩子就可以给家庭多增添一份幸福。我们或许会担心,一些父母生孩子不过是为了压榨或者虐待他们,即便有这个可能,也不能证明别人就能替这些孩子做出更好的选择。当多生孩子也会增加其他家庭的负担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更为严肃的讨论:孩子多了,学校和医院可能更拥挤;公地、清洁水、能源会相对减少;全球变暖进程加快。这些被认为是由人口过多所导致的后果,通常被称为“公地悲剧”。而长久以来,是否需要以控制人口的方式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围绕着公地悲剧解决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价格方法来解决此类的问题。有时候征税可以使人们关注某项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如果不征税人们就可能完全漠视这些成本的存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这项征税活动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但是此类策略也存在问题,因为要确定这样的税种,其前提是要达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而诸如能源的获取、公地的使用,以及水权的归属等地方性问题,也需要依靠地方性的政治协商来解决。虽然从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相适宜的制度建立起来以满足相关政治行动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商讨确实可以解决很多争端,同时阻止人们将成本转嫁给其他人。医院和学校的配给也可以通过地方或全国性的政治协商予以解决。一个恰当合理的政治体系,应当包含某种限制家庭规模的经济或者社会因素,而如果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人口控制,则可能是解决公地悲剧以及相似困境的较好举措。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外来者,包括外国政府、国际机构或者基金会等进行的人口控制会起作用。这些机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所谓它们正在帮扶的人民的生活,它们的所知也经常极为有限。
很多以控制人口为名的活动都对穷国造成了伤害,甚至酿成严重的灾祸。印度就存在极为严重的滥用控制人口措施的现象。在印度,政府推行了所谓的自愿绝育政策,但事实上,这项政策常常变成强制性措施。虽然直接推行绝育政策的是印度的政客与官员,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不但鼓励这样的举措,还为之提供智力和财务支持,因此,对于这种人口控制手段的滥用,它们也负有很大责任。
尽管世界末日的预言弥漫,但人口爆炸性增长却并未让世界陷入饥荒和贫困,正相反,过去半个世纪的真实情况是,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了人口爆炸,但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口实现了大规模脱贫。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发生?我们最初的预测为何会错得如此离谱?
当然,当时也有正确的预测。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当初就不断地挑战“末日说”,他所做出的预言今天看来都惊人的正确,其大量的论证今日也广为人们所接受。在其著作《最终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 )中,西蒙称,土地和自然资源终有一天会被耗尽,它们都绝非繁荣的真正源泉,繁荣的源泉是人。每新增加一个人,虽然多了一张嘴,但也增加了一个未来的劳动力,从长期看,这将使得平均收入与人口规模失去关联性。不但如此,一个新人所带来的,还有创造性的思维。这些新增人口所带来的某些新理念,不仅可以为他们的雇主带来利益,也会造福全人类。如果说多了一倍吃饭的嘴同时多了一倍干活的手相当于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些新增头脑的新创意新理念,则可以提高每双手的工作效率。当然,不是每个新生人口都能变成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亨利·福特,也并非每一种新的理念都能够造福全人类。但是,理念可以共享,所以不必人人都是天才,只要一种有益的理念在各地得到实践,那么受益的就是使用它的所有人,而绝非仅仅是这种理念的创造者本人。更多的婴儿诞生,意味着人人都要承受新增人口的成本,比如拥挤的学校和医院。但是,人的增加却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而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基础,也是人类摆脱贫困与病痛的工具。这些新的益处累积起来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所需要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健康改善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双重好处:不但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带来了全球知识与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
经济学家兼人口学家戴维·林在美国人口学会2011年的主席报告中指出,过去50年是全球历史上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繁荣。这有赖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在儿童死亡率出现前所未有下降幅度的同时,家庭减少了生养的子女数量,而更关注生育的质量。在以前,那些可能生下来就死掉的孩子,如今再也“不需要”降临人世,这不但减少了妈妈生育的痛苦与危险,也使得父母双方都避免了可能的丧子之痛。之前我们总说,儿童死亡率降低的最大好处是避免了亿万儿童的死亡,但其实它也让人们得以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事实也的确如此,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生活方式因为养育子女的减少而发生了改变。她们有了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比如接受再教育或者走出家门就业。她们也得以把更多的资源和时间投入现有孩子的养育和发展之中。
儿童死亡率下降意味着父母在减少子女生育数量的同时,其能够长大成人延续香火、继承财产的子女人数却没有减少,与此同时,父母们的付出和所经受的风险大大下降。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大概10年的转变过程,否则也就不会有人口爆炸了。但也正因为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所以人口爆炸也只是一个“历时较长的短暂现象”。这段历史大概是这样的:最初,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平衡,然后是出生人口大大超过死亡人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出生和死亡人口重新平衡,但是新的平衡是建立在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都比1950年大大降低的基础上。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1960年达到了2.2%,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了一半。在死亡率大幅下降和生育率开始下降的这段时间差内,大量人口出生,世界人口大幅增长。一开始,这些人处在儿童期,需求远远大于产出,然后他们进入成年期,开始有生产力和创造力,最后他们进入老年阶段。如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退休。
林也强调,在人口增长的挑战面前,世界经济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是本书一直在阐述的主题之一:社会本身会想方设法化解新问题。这一方面是依靠新的生产方式,毕竟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创新的头脑;另一方面是依靠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的创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并使得食物的生产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全球化使得生产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保护,新的能源替代品也已出现。价格体系在建立激励机制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如果非再生资源变得极度稀缺,其价格就会上升,于是人们要么减少使用量,要么寻找替代品;或者是推动直接的技术变革,找到一种无须使用这些能源的新生产方式。
不过,经济学家指出,盲目地相信价格机制会贻害无穷,事实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是,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批评家都一致相信,如果重要的资源没有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人们无须成本就可以使用,那将是更为危险的事情。没有价格,就不会有动力减少对这些商品的使用。这方面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全球变暖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变暖将成为对全球经济持续性增长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
绝大多数当年的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对人口爆炸结果出现了误判,由此做出的错误决策给成百上千万人造成了巨大伤害。20世纪人类有许多重大的知识性和道德性错误,在人口问题上的误判与政策失误,是其中最为重大的错误之一。
避孕本身并没有错。避孕行为使得夫妻可以控制生育率,让自己和子女都从中受益。避孕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对生育率的有效管理,也让全世界女性受惠。和很多其他类型的创新发明结果一样,最早从避孕中受益的仍然是富裕国家的人们,而这也就同时带来了一项新的全球不平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新的避孕手段以缩小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就顺理成章成为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如同抗生素和疫苗接种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进步,避孕措施也被认为有同样的作用。不过,那些建立在强迫之上、以牺牲千百万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政策和手段是极其错误的。而那些富裕国家,也在帮助穷国的名义下做了帮凶。富裕国家本应该帮助穷国,将它们所造成的不平等消灭掉,结果却是在全球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有的伤害是由错误的判断所造成,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都过于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诊断和处方的可靠性。但是,这些错误的根源恐怕还是在于富裕国家本身,它们惊恐于一个可能有更多穷人的世界,更担心人口爆炸会引发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浪潮。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见,国家的繁荣发展并未降低美国的贫困程度,至少在1975年之后的确如此。但是从整个世界来看,人类的确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人均工资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在1975年以后,这两个国家为降低世界的极端贫困率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印两国,尤其是中国,亿万民众摆脱了长期的的贫困状态,堪称有史以来人类最为伟大的逃亡。
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上是清晰的,而由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未遭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及其后果却有两方面的忧虑:一是对于全球贫困状况的评估和衡量我们缺乏明确有效的方法;二是我们还并没有搞清楚那所说的每天生活费用在1美元或者1.25美元以下的人群到底是哪一部分人。
在地方社区中区分贫富较为容易。持发展观点的实践者经常引入“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法来对当地的生活水平进行评估。运用这种方法,当地的村民会被召集到一个地点——比如一棵大榕树下——由他们将村庄的基本情况:粮食收成、村民的主要职业和活动、村庄的饮水情况、主要的交通工具以及村民的构成等告诉数据收集者。如此,残疾人员以及孤寡老人就经常会被认定为是贫困人口。富裕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对于一个家庭需要多少钱才能生存下去,社区的民众总是乐于给出热情的答复。设立贫困线则要比这种数据调查更为复杂,因为贫困线的设立意味着某些人会得到特殊的对待,比如补贴之类就只会给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不过,美国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贫困线是有办法计算的,同时经由政治辩论程序,也会得到定期不定期地修订或调整。印度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做出评估之后,该国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最初的贫困线标准,后来这一标准被印度政府采纳,然后不定时地进行修改。在印度,官方贫困线由印度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每当现有的贫困线显得过时或者不再为大众认可,印度计划委员会就会通过一个被称为“专家委员会”的机构对贫困线进行调整。
无论是印度的贫困线还是美国的贫困线,都是在民主体系中经由讨论产生的,此外,媒体和相关利益集团也会参与贫困线的制定。这些因素使得贫困线具备了非常高的国内合法性。然而,其他很多国家的贫困线,甚至大多数国家的贫困线,都不具备这样的合法性。对于很多政府而言,所谓减少贫困纯粹是一种口号或表面文章,这些国家的贫困线都是在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鼓动下才设立的,并非是基于国内实际情况的商讨,而经常是出自世界银行善意提供的指导。
由世界银行所设定的贫困线或者依据世行的方法所设定的贫困线相对来说是可靠的,至少外部的专家对此非常认可。但实际上,依据这种方法制定的贫困线,通常表示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仅仅满足温饱所需要的收入水平。这样的贫困线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缺乏合理性,而是缺乏合法性。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国的国民会认可这种对自己贫困与否的划分,而贫穷人口对此的争议更大。实际上,国际机构设定这些贫困线的初衷,不过是为了统计方便,其对贫困状况的评价,也多是源于自身的需要。
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线是这样计算的:首先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选出一部分代表,然后将这些国家的贫困线加以平均,进而得出全球贫困线。这个贫困线最初的标准是1美元一天,不过,2008年,世界银行将这个标准提升到了1.25美元一天。由于各个国家的贫困线都是以本地货币为单位制定的,因此在计算平均数时,这些贫困线数字就必须先换算为同一种货币单位,这就用到了我之前所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20年前,世界银行最早制定的贫困标准是一个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超过1美元(以1985年美元计),或者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 460美元。由于选取的国家样本变化等因素,最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25美元(以2005年美元计),或者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 825美元。贫困线制定出来后,会再依据汇率换算成不同的货币,这样就可以采用与国际标准等值的本地货币来计算各国的贫困人口。依据这种方法,世界银行可以计算出各个国家“全球性”的贫困人口数量,继而算出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数以及整个世界的贫困人口数。
1990年以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计算方法和标准基本没有改变,我们现在可以在世界银行查阅到1980~2008年的全球贫困情况变化数据。这一数据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及。从第一章中图1–6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每日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的人口,已经从1981年的15亿人降到2008年的8.05亿人。由于同一时期,数据所统计的全球人口增加了近20亿,因此,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要比贫困人口绝对数的下降速度快许多,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原先的42%下降到了14%。这一成就,可以说完完全全是由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推动实现的。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数据排除在外,那么在1981年时,全球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是7.85亿,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是7.08亿。同样,如果不包括中国人口,这一时期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由之前的29%下降到了2008年的16%,相比于包括中国人口的下降速度,这一数据变化实在没什么惊人。
印度是另外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大国。同一时期,印度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口从2.96亿下降到了2.47亿,贫困人口比例则由42%下降到了21%。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这两个大国的快速发展对减少世界贫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减贫问题上却遭遇了重大失败:2008年,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7%,而在1981年,这个数值为43%;并且由于非洲的生育率并未和亚洲的一样出现下降,这一地区的贫困人口总量从1.69亿增加到了3.03亿,翻了几乎1倍。
非洲虽然幅员辽阔,在地图上非常显眼,但是相比于南亚和东亚,其人口密度要低得多,因此,虽然在减贫方面相对表现较差,但是由于总人口少,其对全球减贫的拖累远不能抵销亚洲国家的正面作用。我们也要注意不能总是贬低中国的成就,不能老犯这样的错误。贫困问题的悲观主义者,尤其是援助行业内的人士经常说,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并未对全球减贫做出多大贡献。贬低中国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所发生的改变不是一出独角戏,而是一场涉及13亿人口的巨变,任何对中国减贫贡献的轻视不过是在说中国人没有埃塞俄比亚人、肯尼亚人抑或是塞内加尔人重要罢了。每一个国家都理应得到与其地位和价值相称的研究与评价,当我们在关注全球生活变化并试图做出评价之时,每个人,不论生于何地,其价值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小国就应该得到褒奖,生在一个大国就要受到贬低。全球贫困概念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理念,对它的衡量与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
那么,这些贫困数据究竟是否可信?我之前已经简单介绍过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除了缺乏各国当地的民主商讨意见之外,这个评价体系是基本可信赖的。当然,这种方法一直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参与了这些数据的创建,但对这些数据一直同时有所批评。和很多的数据创建者一样,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我们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小心谨慎。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对全球减贫总体性特征的把握是正确的。中国与印度的快速发展绝对真实,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速可能有所夸大,然而这绝不会影响到贫困减少的总体方向,尤其是在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洲数据的真实性往往较差,不确定性非常多,但是其贫困状况并无好转的结论完全可以被我们所掌握的其他证据证明。例如,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非洲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也较为缓慢。不过,除了这个大体的趋势,世界贫困状况的确不是一个可以明确说清楚的问题。
全球贫困评估体系的一个缺点是它过于依赖购买力平价汇率,因为购买力平价汇率存在“马麦酱问题”等多种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依赖这种汇率的贫困评估极易招致批评。另外一个缺点是每个国家对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统计都可能存在误差。贫困线本身是否合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购买力平价汇率的统计计算并非每年都有,而是不定时地开展。过去的三次统计分别是在1985年、1993年以及2005年,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但结果尚未出炉。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参与这一汇率的统计。中国在2005年之前都没有参与到这一统计之中,而我们知道,以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它参与与否对结果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前期的购买力平价估测是基于一个不完整的数据,虽然这比胡乱猜测要好很多,但可靠性还是远远不够。这些原因的存在,或者仅仅是评估方法本身的问题(对此我们无法确认),导致每次购买力评价汇率被修正时,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都会产生一种令人警觉的趋势性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单个国家的贫困人数已经是够糟糕了,更何况它还会影响整个地域的数据。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修正使得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穷困,而拉美国家的贫困程度则被降低。这引起的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变化: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比例一下子从39%增加到了49%。
2005年,随着数据的再次更新,世界银行估算出的世界贫困人口又增长了近1/3,更多的亚洲和非洲人被定义为贫困人口。这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调整了贫困线。贫困线的变化也反映出贫困人口数字的不可靠,与此同时,世行将自己设定的贫困标准作为判断减贫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也引发了不满。当然,所有的变化都是统计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变得更穷或者更富有。但是,这样的数据变化会使得国际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方向与口号都转向新的为它们所“见”的最为贫困的地区;而这也是贫困数据统计之所以非常重要的诸多原因之一。在1993年数据更新之后,非洲成了新的最受关注的贫困地区。贫困数据的调整导致全球的贫困地图像一条变色龙,不断变换颜色,而所谓救助与注意力向最贫穷国家的转移或许只是在追逐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幻象。
不过,基础数据的修订并未对全球贫困状况的发展趋势产生明显影响。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的贫困下降速度仍然可能因为数据的修订而被低估,真实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速度可能比官方所公布的还要快。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其中既有技术原因,也有深刻的政治因素。
即便是贫困线已经划定,要弄清楚每个国家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仍然是一件极难的事情。相关的统计往往采取家庭调查方式,即随机选取一些家庭样本,了解它们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然后得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人口数量。国民收入核算部门对整个国家的总体支出和收入有一个独立的估算,它们会将家庭调查得出的结果与其独立的估算进行对比。不过,在很多国家,对比的结果常常是两个数据大相径庭,家庭调查得到的总收入往往大幅低于统计人员所估算的数额;而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数据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开展入户调查,人们会说,他们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并没有赶上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但是一般家庭的收入却增加很少甚至没有增加。之所以有此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对于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不平等也几乎必然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但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的是,印度的家庭数据一直和总体数据相互矛盾。这两种统计数据不可调和的问题不仅仅在印度存在,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在印度,这种数据相互矛盾的问题所引发的讨论极为尖锐。政治偏右人士认为总体的数据是可信的,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所使用的贫困数据统计方法都低估了贫困人口的下降程度。他们称,调查者存在作弊行为,没有真正地深入调查,其所得到的数据,不过是坐在树下或者茶馆里胡编乱造出来的。政治偏左人士则更认可样本调查数据,他们称,如果被调查者不认为贫困减少了,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贫困真的减少了。这一派认为印度的国民收入核算存在多种缺陷,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调查的数据都是弄虚作假得来的。毫无疑问,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的争论提醒了我们,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往往缺乏坚实与充分的事实基础,人们不过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对事实做出了偏好选择。这一现象背后的事实是,印度政府至少在言辞上变得越来越亲近商业阶层而越来越疏远穷人。因此,印度政府必然要大力证明其经济增长使得人人受益,而绝非只是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中产阶级捞到了好处。而否认这些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就可以使得富人们直接无视穷人的存在。
细微的变化可以有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所熟知的一个印度事例就是极好的证明。印度统计研究所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名叫P·C·马哈拉诺比斯,他在家庭调查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过数次实验后,马哈拉诺比斯确定在进行家庭调查时,应当询问每个家庭在过去30天的具体消费情况,比如吃掉了多少米和面等。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全国抽样调查一直沿用马哈拉诺比斯的30天调查规则,不过,其他很多国家将调查期缩短为7天,因为它们认为受访者很难准确记住很久之前的消费情况。不少人认定,正是由于30天的调查期过长使得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一些消费支出,因此贫困的问题被夸大。这样的观点使得7天调查期得到认可采用,而结果果然如之前所料,依据这种方法统计到的家庭平均日常支出额增加了。这一微小的统计技术变化直接让印度的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也就是说,有1.75亿人因为这个统计方式的变化而脱贫。但是,调查天数的变化肯定只能是让统计人员兴奋,因为受调查者报告期缩短可以让统计者获得更多的细节。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以完全改变对贫困的统计与认知的确让人激动:只要改变统计手段就能实现减贫,这比靠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减贫要简单多了!
不过,7天报告期的调查手段在印度并未得到长期使用。马哈拉诺比斯后来又改进了30天报告期的统计方法,使其准确度有所提高,并且还经常优于7天报告期的统计方法,于是30天报告期又重新被印度采用,这也让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但对于印度这样的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还有比找到一种好的统计方法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大量接近贫困状态的人口,他们可能是位于贫困线以下,也可能刚刚高出贫困线。若贫困线稍微往下降低一点,则就有千百万原先被计为贫困的人口脱贫,而如果贫困线稍微上调一点,则就有千百万人从非穷人变成穷人。也就是说,贫困线的任何变动,或者是贫困评估方式的细微改变,都会对贫困人口的统计结果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贫困线如此敏感,影响了整个贫困评价的效用。而正是因为这条贫困线的位置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就不清楚这条贫困线到底应该设在何处。说得更粗暴一点,真实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把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贫困线这样一个数字来决定显然是一个错误。
在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米考伯对贫困线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发现:“年收入20英镑,如果每年花销19英镑19先令6便士,结果是幸福。年收入20英镑,如果每年花销20英镑6便士,结果是痛苦。”这段话非常有名,有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段话太蠢了。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么多的事情寄托在如此细微的差别之上?为什么有些人的支出只是稍微比贫困线低了那么一点,就可以得到特别帮助或者是世界银行的关照?而有些人的支出只是比贫困线高出一点却完全得不到帮助,而只能依靠自己?当我们对贫困线到底是什么还不够了解时,当我们在收入的衡量上还有很多困难时,做出米考伯式的判断便是蠢上加蠢。我们应该关心那些更穷困的人,但绝不应该以任何的分界线为界,对处境相近的一类人给予截然不同的对待。
最后要注意的是全球贫困线问题。多数人认为生活在美国或者欧洲是不可能一天仅靠1美元生活下去的。尽管从来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欧美也不在全球贫困统计范围之内,但认定人们不能以一天1美元的标准在欧美甚至其他国家生存,的确削弱了这条国际贫困线的权威性。毕竟千百万印度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过22卢比,以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成美元还不足1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意义在于,它表示在不同的国家同等价值货币意味着同等的购买力。所以,假使印度人可以一天靠22卢比生存,并且还不算是最差的境况,那为什么美国人不能一天只靠1美元生存?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否存在令人全然信服的答案。在美国有三样重要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是印度的贫困线所未能包括的: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的费用。此外,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基本不需要供暖,同时在穿着上的花费也较美国的少很多。在自己居所附近工作的印度人,其交通花费基本为零。如果在美国这三方面的花费都能排除,那么一个“没有水电通信与世隔绝”的美国四口之家,一年靠1 460美元也能活下去。当然,这些钱只能用来买足够便宜的食物,比如散装大米、燕麦、豆子以及少量的蔬菜。最近的一项研究还列出了一份“最低需求”清单,依照这个标准,一个美国人可以每天靠1.25美元生存下去,或者说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有1 825美元就能生活下去。不过,全球贫困线的支持者也须注意,即便是在印度,一天仅有22个卢比也只能让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印度的穷人及其子女,即便能够靠这点钱维持日常温饱,却无法不成为世界上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人。
经常有观点认为,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富人抓住了新的机遇而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却没有得到多少益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这些人运气足够好,能够生活在欧洲或者北美这样的发达地区,享受到这个崭新的、相互密切联系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与此同时,贫穷内陆国家的人们却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状况也不佳。全球化的种种好处,完全没有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全球化使亚洲劳动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融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即便他们无法移民至发达国家,以前那些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如今也已经大量转移到了亚洲地区。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那么亚洲人的工资水平就会上升,而美国和欧洲人的工资水平则会下降,这样,世界整体上的工资差距将会缩小。全球化也使得资本拥有者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如果富裕国家资本相对丰盈,穷国资本相对稀缺,则世界的开放会使得富裕国家的资本家更为富有,穷国资本家的富裕程度则可能下降。而如果资本家变得更为富有、工人阶层变得更为穷困的话,在富裕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就会增加,在贫穷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则会出现收缩。(当然,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化。)
在本章的开头,我所提供的数据就显示出各个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或者说得温和点,各国的平均收入差距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缩小趋势。因为几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迅速,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的工资水平正在远离贫困向中产阶级的方向靠近。对于缩小全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而言,这几十亿人口是可以降低全球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用一个平均数来衡量全世界人口的贫富程度,因为这忽视了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中国人和印度人平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保证中国和印度内部的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快速增长的好处。用我之前奥运会的比喻来说,就是虽然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从游行队伍的尾端向中间部分进发,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举着中国旗子和印度旗子的个体都已经走到了队伍的中间。印度高科技城市中的巨富可能早已经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端了,但贫穷的农村劳动者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如果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就可能使得整个国家所取得的进步成绩黯然失色,而世界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也会因此扩大。
第五章告诉了我们美国国内不平等的发展情况。虽然美国只是个例,但是一些影响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比如新科技和全球化等,也会在其他国家或者至少在其他富裕国家存在。另外有证据显示,在贫穷国家内部,并非所有的人都享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虽然我知道除了具有难以衡量的共同特性之外,全世界很难有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全然相同,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从总体的趋势来看,全世界的收入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美国的情况有自己的特点,其贫富差距的总体水平以及近期贫富差距的爆发性扩大,尤其是顶端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等都与别国有不同之处。在其他一些富裕国家,顶端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21世纪多数时候是在下降的,且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近期所出现的顶端人群收入增长现象在规模级别上也不及美国,出现的时间也较美国要晚。但即便如此,美国也绝非唯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国家。
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地区不平等问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城乡人民之间的差距推动了人口的迁移,这当然会有助于降低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由于中国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有超过1亿的外来打工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和家人分离。在印度,像南部和西部这样的地区发展得要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但其全国性的贫富差距扩张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对两个国家收入所得税的研究显示,中国和印度收入最高1%人群所占有的财富,虽然数额只有美国同类人群财富数量的1/3和1/2,增速却非常快。当然,有证据显示,其他几个大国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缩小的情况,比如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传统上都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使得整个世界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
在不少富裕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近几年变得更为严重。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战争、通胀以及税收等吞噬了富人阶层的大部分财富,多数国家的顶端收入人群收入都出现了下降。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语世界的几个富裕国家,比如美国,其收入最高1%人群的财富出现了迅猛增加,但是欧洲其他国家(除挪威外)以及日本却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收入最高的这1%人群变得越来越富有时,意味着其他99%的人的财富可能连国内平均值都没有达到。在不同的国家,收入最高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例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各国其他99%人口的生活水平进行排序,那么这个顺序可能与以全部人口平均收入为准所做的排序有所不同。
法国与美国的比较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近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远不如美国迅速,但是如果对两国占99%比例人群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会发现,法国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换句话说,除了收入最高的那1%人群之外,剩余的法国人日子要比剩余的美国人日子过得好。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与以非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美国顶级薪酬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全世界薪酬市场的发展,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在这样的市场中轻易谋职,法国、德国或者日本的管理者则无此优势。一个更为温和的解释是,全球化为顶级的英语国家人才创造出了一个庞大而多金的市场。比如,如今,歌唱家和体育明星也进入了CEO的全球俱乐部。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人口的超高收入是他们开拓新的全球市场所获得的回报,而不是美国的CEO们拿钱太多以至于其他英语国家的人纷纷仿效所致。
对于所有的富裕国家来说,技术变革与贫穷国家劳动力低工资的竞争是它们要面对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和美国一样的国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最近有不少国家出现这种迹象,尤其是中位数以上的人群收入出现了极大的扩张。就业与收入出现两极化现象,并且在富国越来越普遍:很多中等收入的工作为机器所取代,或者被外包出去,而低收入的服务性岗位则大量存在。这种崭新的两极化限制了底层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扩张。另外,底层收入人群中单亲家庭增多,顶层权势人群中权势夫妻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的趋势。欧洲在税收体系和再分配体系方面较美国更为全面,也更注重限制贫富差距的发展,但是这些似乎都未能阻止不平等事实上的持续扩大。
这些国家各不相同的情况,对于世界整体的贫富差距而言意味着什么?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否会抵消几个人口大国在降低财富不平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各国的平均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同时一般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是不是意味着世界在整体上变得更为不平等了?
这些问题,只有最后一个有确定的答案——世界并没有变得更为不平等。不同的国家大小规模千差万别,近些年来,几个人口大国经济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了平均水平。当按照国别进行研究时,我们将几内亚比绍这样仅有150万人口的小国与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等而视之。几内亚比绍和很多其他的非洲国家整体表现不佳,这只能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但我们要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否在扩大,因此,这种国家间的对比所产生的结论对我们毫无用处。
那么,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否会影响世界整体的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世界不平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处在世界整体收入分配最顶端的这部分人而言。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上多数的不平等来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而非这些国家内部的差别。比如我们再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为例。相对于其他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样的发展虽然也带来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整个世界也因此变得更为平等。而只要中国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结论就会一直成立。详尽的估算以及多项证据都说明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尽管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是全球贫富差距并未恶化,或者说正在缓慢下降。尽管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全然确定,但这样的结论却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数据是否真实,它们的增长是否真如其官方所宣称的那样迅速。而因为要对中印两国进行对比,以及将中印两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这一不确定性也将再次被放大。
最后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真应该关注全球的贫富差距吗,如果应当,原因何在?就一个国家而言,内部的贫富差距事关公平: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管自己愿意与否,都要缴纳赋税、遵守法律、执行政策,他们理应得到与其义务相对应的合理回报。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经写道:“一个政治共同体要想对其公民实行统治,并要求他们效忠与遵守其制定的法律,就必须要对所有的公民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应当承认,对于收入分配如何才算公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而美国严重并且在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否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在进行事关收入差距这样的讨论时,关注是否需要有所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应该是这类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整个世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为人们所拥戴的政府,对于全球间的收入差距,虽然也会有人认为不公平,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府出面应对。对国内收入差距的评估可以为国内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但是对于全世界的收入差距评估并不能为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实际上,在全球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并无任何官方数据,而这样的话题或许有待对此感兴趣的个体学者进行研究。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共识,也有很多争论。虽然没有世界政府,但我们的确有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银行之类的世界性机构。这些机构的政策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民众的收入,它们也确实经常像一个政权一样,用行动支持那些公平权利受到损害的人。这些机构都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进行全球征税,也无法建立全球性的再分配体系,但是它们的确有行善或者作恶的潜能,而这足以使得它们至少对全球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个世界并非一个联合体,然而也绝不是由一些相互隔绝、毫无联系的国家所组成。
今 天世界上仍有近10亿人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仍有千百万儿童因为出生在物质匮乏之地而死去。在印度,消瘦症与发育障碍仍在损害着近半儿童的身体,这些人在大逃亡中掉队。极端的不平等会催生出消灭不平等的方法。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大逃亡,而逃离贫困与匮乏的益处以及掉队的可怕之处,无须我在这里赘言。在南亚和东亚,一些国家已经抓住机会奋力追赶了上来,成百上千万的人口因此得以摆脱贫困与早夭的命运;但是严酷的差距依然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富裕国家尝试以对外援助的形式去缩小差距。对外援助以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为目的,是一种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的资源流动。早先资源的流动是反向的,富裕国家以战争掳掠和殖民剥削的方式,把资源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后来,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向贫穷国家输送资本以寻求收益,但仍不会把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作为目标。经由贸易,原材料产品从穷国出口至富裕国家并被制造成工业品,但是极少有贫困国家能够依靠原材料的出口而脱贫致富。很多贫穷国家的最终境遇,不过是一方面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内部出现了不平等。与上述历史相比,对外援助的性质全然不同,它的设立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受援者获益。
以前,落后者所期望的不过是学习先行者的经验;对他们而言,既得利益者没有把落后者前行的道路堵死已是万幸。认为走在前面的幸运者应该回头去帮助掉队的群体是一种新的理念。对外援助是实实在在加快了人类的大逃亡进程,还是因为里面掺杂了各种动机、政治因素或非预期后果而起了全然相反的作用?这些是本章力图厘清的问题。
关于全球贫困的一个惊人事实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变魔术一样把钱转入世界上贫困人口的银行账户中,那么贫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消灭。2008年,世界上大约有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少于1美元。这些人实际的平均生活费是0.72美元一天,即相较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他们只要每天多赚0.28美元就算脱贫。0.28美元乘以8亿只有2.2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只要付出不到2.5亿美元就能让他们的生活标准达到每天1美元。如果美国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情,算上孩子在内的每个美国人只需要每天拿出0.75美元即可,如果不算孩子则需要每人每天拿出1美元。如果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成人也参与进来的话,那每人每天出0.5美元就足够了。这点钱并不算多,而消灭贫困实际所需的钱数其实更少。几乎世界上所有贫困国家的食物、住房或者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低于富裕国家,比如对生活在印度的穷人来讲,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抵得上在美国2.5美元的购买力。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每个美国成年人能够每天捐出0.3美元,就可以消灭贫困;如果能够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年人都加入进来,那想要解决全球贫困,只需要每人每天捐出0.15美元。
但人们很难相信全球贫困的持久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愿拿出这一点点钱。这一章的主题之一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类似这样的计算其实完全没有找到消除贫困的正确途径。我们将看到,贫困问题的根源绝不在于区区0.15美元,就算我们将每人拿出的钱增加到0.3美元甚至1.5美元,贫困问题也不会因此就被消灭。
每天1美元这个贫困线标准只能满足养活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改善健康状况或者疾病治疗等更重要方面的花费都没有被包括在内。一些网站会就一笔善款在某些特定方面的效用做出自己的估算。比如由哲学家托比·奥德经营的网站givingwhatwecan.org就声称,如果一个年收入15 000英镑的人能够每年拿出收入的1/10,也就是1 500英镑,就能每年拯救1.5条生命,或者每年能够为将近5 000个得了热带病的儿童提供治疗费用。稍后我会对这些数字的立论基础进行质疑,但是应该说,这些数字都是经严肃的估测而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而且相对于成效而言,1 500英镑这样的数字的确也不大。但更多粗枝大叶的慈善倡导者们给出的数字就常常太离谱,比如男演员理查德·阿滕伯勒(我们在引言中提过这个人),他在2000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声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只要17便士(大约0.27美元)就能资助一个莫桑比克孩子的生活。
以上的这些计算,包括我在刚开始时提到的那些认为轻而易举就能消除贫困的例子,其实都可以归为一种类型——我将它们称为援助错觉。这些错觉认为,只要富裕的人们或者富裕的国家多给予穷人或者贫困国家一些金钱援助就能够消除贫困。而在我看来,援助绝非消除贫困的良方,恰恰相反,它其实是阻碍穷人改善生活的一块绊脚石。
我们是怎么计算出每天只用0.15美元就可以消除世界贫困的?既然消除世界性的贫困只需要花这么少的钱,那为什么贫困还一直存在?这里有四个可能的原因:
·道德冷漠:富人对穷人漠不关心。
·缺乏理解:人们关心穷人,但是并没意识到为消除贫困做点儿事其实很简单。
·援助本可以是有效的,但是它被误用了,当前的援助是无效的。
·援助通常是无效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是有害的。
我将讨论以上所有的原因。不过让我们先从道德冷漠和贫穷是否容易消除这两个问题入手。
有没有这种可能:富人的确冷酷无情,他们拒绝做出哪怕是微小的牺牲去拯救那10亿完全陷入贫困的人。如果贫困是降临在他们的朋友或家人身上,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无情,但对于那些与他们完全不一样或者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人,他们或许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提供帮助的义务。
不过,亚当·斯密并不这样认为,在其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发生了大地震,那些没有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是否会拒绝动动小手指,去拯救那1亿从未谋过面的中国人的性命?他自己的结论是:“即使是一个腐败堕落之极的世界,也绝不会存在这样以他人之苦为乐的恶棍。”与斯密同时代的大卫·休谟则说,(18世纪的)全球化让人们更加富有同情心并且更加愿意去帮助千里之外的人。如今的时代,全球化程度更为深广,人们的同情心和为他人提供帮助的意愿理应更为强烈才对。
有观点认为,距离会导致人们在道德责任感上的差异。一个过路人会拒绝救助落入浅池中的孩子,哪怕救这个孩子只要付出稍稍弄坏自己衣服这一点点的代价。人们拒绝救助非洲儿童的理由也与此类似。但哲学家彼得·辛格一直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对于欧美人而言,一个非洲儿童虽然远在天边,但应当施以援手的道德责任并不会因为距离远近而有所不同。因为现实中有诸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这样的国际慈善机构存在,它们能够代表我们战胜距离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其他的援助机构有效,那么拒绝援助和拒绝帮助一个快淹死的孩子这两件事在道德层面上便是同样的。在1971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的那场战争中,辛格记录了当时战争难民所遭受的苦难,并总结说:“我觉得,对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一点,没有大的争议,我们的分歧在于,是应该用传统的物资救济方式来解决饥荒呢,还是通过控制人口的方式,还是应该两者同时进行?”辛格近年来的著作仍然坚持距离不应该造成差异这一主张,而如今的一些网站,比如givingwhatwecan.org和givewell.org等也在帮助潜在的(但同时可能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援助者审核国际慈善机构,它们会选出那些在减少饥荒和改善健康方面卓有成效的组织,然后将其推荐给潜在捐款者。关于援助责任的伦理讨论自然没有什么争议,但真正的问题并非道德层面上的,而是现实层面上的,即是否“我们”(世界上非穷困群体)有能力去救助“他们”(全球的穷困群体)?
显而易见,这一章开头部分所说的只要每天捐0.15美元就能消除穷困的观点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实际上,许多人对这个估算的第一反应是0.15美元过少,因为捐助过程毫无疑问会产生损耗和管理费,所以要消除贫困,我们可能需要一天捐助0.5美元甚至1~2美元。在这里,我们的道德责任并不是体现在0.15美元这个小钱上,因为相对于所拥有的,我们所付出的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道德责任应该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已深陷如此困境的人们更不能这样做。认为出钱就可以消除贫困的观点,不论出钱多少,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只要穷国得到更多的钱,它们的情况就会更好。但矛盾也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因为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给予穷人比目前水平更高的援助或者继续以现有的水平进行援助,他们的情况不但不会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糟糕。
同很多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对外援助额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重的确较小,但仍比每人0.15美元的标准要高出许多。2011年,全部富裕国家所提供的官方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1 335亿美元,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个穷人每天能得到0.37美元的救助。按照贫穷国家的购买力计算,这笔钱相当于只比1美元稍微少一点。这还没有把私人慈善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巨额援助款考虑在内(大约有300亿美元)。如果这些来自富裕国家私人和政府的钱能够直接交给那些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其金额将足以消除世界贫困。可这一切并未发生,这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先弄清楚这一点,才能对援助这件事情有更为正确的认识。
我们前面最开始的计算实际上是将对外援助理解为一种“液压流动”:如果在一端注水,那么水就肯定会从另一端流出来。治理全球贫困与拯救垂死儿童的生命被简单地当成了一个工程学问题,很多人以为这跟修水管或者修汽车一样。修车是这样的: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变速器,算算多少钱;换两个新轮胎,一个多少钱,工时费多少钱,就是说只要给钱就能解决问题。以此类推,他们以为只要知道一顶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可保护儿童免于疟疾)价值几美元,一剂口服补液价值几美元,接种一次疫苗需花费几美元,然后设法提供相应数额的资金,孩子们就能够得救了。正如在工程、项目和机械装备上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样,经济增长才是消除贫穷的最好方法。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增长与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高度相关,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计算出一个国家若想要经济更快增长并更快地消灭贫困,到底需要投入多少新的资本。
很多人到如今还对这样的计算方法深信不疑,但实际上对这种计算本身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彼得·鲍尔在1971年就做出了重要的论断:“如果除了资本以外,其他所有发展条件都已经具备,那么资本会迅速在本地自发生成,或者通过商业合作方式从国外流入国内的政府或私人部门,然后通过税收增长或企业的利润增加而进一步增长。如果发展条件并不具备,那么援助将成为仅有的外部资本来源,而它必然是不会有产出的,因此也是无效的。”今天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无论在有效性还是规模上都已绝非鲍尔当年所能想象。如果鲍尔的说法在1971年是对的,那么现在就更加毋庸置疑。
在这里,对外援助所存在的一个核心困境凸显出来:当受援助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都具备之后,援助就不是必需品了;而当其内部条件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时,援助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并且援助还有可能使某些不利于发展的内部条件固化,起帮倒忙的作用。对这一困境的忽视会导致很多后果。各类援助开发机构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之中:只有当援助被需要最少的时候援助才是有效的,而援助者总是坚持让那些需要最多援助的人获得援助。虽然鲍尔只是在谈资本之于投资与增长的作用,但其观点适用面其实更广。如果贫困不是缺乏资源和机会的结果,而是由于失败的体制、失败的政府和独裁政治,那么给贫困国家更多的钱,尤其是给贫困国家政府更多的钱,就可能固化贫困,而不是消除它。以液压流动的理论去理解援助是错误的,治理贫困跟修理汽车完全是两回事,跟在浅水池里救落水儿童也完全是两回事。
在今日之世界,援助之所以没能消除全球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实它根本就没想要消除贫困。世界银行举着消除贫困的大旗,但是它的大部分援助资金都不是通过像它本身这样的多边组织来发放的,而是从一国流向另一国的“双边”援助,而且各个国家对所接收到的援助也有不同的具体投向。近年来,一些援助国已开始强调援助的目的是消除贫困,比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就是其中最早提出此目标的组织。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援助的具体投向并不是根据收受方的需要确定,而是根据援助国的国内与国际利益而定。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这些援助国是民主国家,它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尽管在许多国家的内部比如英国,其民众对消除国际贫困表示了强烈支持,但在进行具体援助时,它们必须平衡许多因素,比如需要考虑政治联盟的利益;又比如援助国在它们的前殖民地国家仍有重要的利益,因此在援助时需要考虑维系好与它们的关系。援助国的国内利益考量,不仅要回应国内公民的人道主义关切,还要权衡国内的商业利益,因为对国外施以援助既包含机会(可以更好地销售商品)也存在风险(需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不过,即便有各种利益纠葛,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还是宣称要实现一些总体的目标,例如要创造一个繁荣民主的世界之类,这些显然和降低全球贫困的目标一致。
先期制定的援助目标其实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重要。援助经常会被用到另外的地方去。所以,即便是原定要购买坦克飞机的军事援助也可能被拿来建设学校或诊所。援助向其他方向的转变其实更值得关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说过:你以为你是在建立一个发电厂,其实你是在资助建立一个妓院。如果美国为了获得政治支持而对一个盟友提供援助,那么这些援助既可能被用在减贫上,也可能被用在健康事业或者教育事业上。因此,根据援助目标将援助进行分类的做法其实没有意义。
对外援助最大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个项目旨在通过富裕国家为贫穷国家提供资金来促进穷国的福利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记录,2011年,各富裕国家政府开发援助的总额为1 335亿美元,23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援助金额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都在0.1%(希腊和韩国)到1%(挪威和瑞典)之间,平均比例为近0.5%。政府开发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迅速,在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年间,该项目的实际援助额翻了1倍。“冷战”结束后,政府开发援助额出现了实质性的削减(这本身就是援助意图的一种反映),到1997年其整体水平已低于1980年。不过,之后政府开发援助又出现了超过50%的增长。从1960年至今,政府开发援助累计的援助金额约为5万亿美元(按2009年物价水平)。
美国目前是政府开发援助最大的出资国,其次是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紧随其后。以援助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这个指标来衡量,美国的援助占其国民收入比例还不足0.2%,排名处在倒数位置,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的荷兰、卢森堡等则处在这个榜单的领先位置。要注意这种衡量方式评测的是各国对援助承诺的履行情况,而并不是以穷国人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标准。
关注援助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的确令人困惑。为什么联合国再三敦促各国的援助额度要占到其本国国民收入的0.7%呢?我们要从池塘里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这跟救人者的收入多少有什么关系?对此有一个类似于液压流动理论的解释:全世界要实现诸如千年发展目标 [1] 这样的发展计划,就需要富裕国家拿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这个计算和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到的那个计算相似,一样不具可信性。还有可能是联合国认为捐款越多越好(对联合国很多成员国的政府来说的确如此,但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倒未必),而国内生产总值的0.7%这一数额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解释:接受0.7%这一比例目标的国家,其国内选民有强烈的要求帮助穷困人民的呼声,但是这些选民无法控制援助的结果,于是只能监督捐款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援助不过是更多地满足了选民自己乐于助人的愿望,而没有考虑其能否切实改善众多贫困人口的生活。
在官方援助以外还存在着众多的对外援助形式。成千上万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参与全球人道主义与经济发展工作,其中规模最大的机构同样体量庞大,年度预算要超过5亿美元。它们本身独立运营同时也为国内机构和国际机构提供代理。据说,它们的活动使得富国流向穷国的援助资金增加了25%~30%,不过,在透明度与效力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巨大。还有部分非传统的援助国,比如巴西、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们的援助不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报告也没有被计入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统计中。
大约80%的政府开发援助都是双边援助,其余的援助则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者抗艾滋、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等多边组织来进行。有观点认为,多边援助因为较少受到国内相关考量的影响,要比双边援助更具透明度和有效率;但实际上,世界银行是不能轻易违背其最大出资国的意愿的,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就被认为是透明度最低并且最无效率的援助机构之一。援助者与援助机构数量庞杂,如今,即便是在一国之内,官方援助也时常要通过各类独立运行的政府机构来推动(比如在美国有50个这样的机构),这不仅给援助总量的统计造成麻烦,也给各类合作带来了巨大问题,而各机构之间也经常出现相互抵触的政策。
如今对外援助已经覆盖众多国家,一些援助者在同时向150多个受援国提供援助资金。援助者似乎更倾向于向国家而不是个人提供援助,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地向更多的国家提供援助,而对穷人到底身在何处并不关注。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从个人受援额度还是受援额度占其收入的比重来看,小国所接收到的援助都要比大国接收到的更多。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大国之中,于是,这种援助者自身引发的“援助分裂”,就成了为何援助不能有效针对穷人的另一个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人均接受援助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萨摩亚(802美元)、汤加(677美元)和佛得角(664美元),而印度和中国两个人口大国,所接受的最多人均援助分别仅为3.1美元(1991年)和2.9美元(1995年)。前面已经说过,世界上大约一半的穷人(至2008年末为48%)要么生活在印度要么生活在中国,而中国和印度在2010年仅仅从政府开发援助中获得了35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额只占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的2.6%。世界上一半的穷人只得到了世界政府开发援助的1/40,这绝对是世界上最为不平等的举措之一。
当然,中国和印度正在快速发展,它们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自己解决贫困问题,而不需要太多的政府开发援助。不过,流入印度的私人投资要6倍于政府开发援助,流入中国的私人投资则57倍于政府开发援助,即有人可能希望捐款能够直接投向这样的能产生最大效能的国家。但我们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萨摩亚和汤加会得到那么多的援助,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任何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种液压流动论观点认为,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此之高的援助就可以使之脱贫,又或者通过援助资金刺激其经济增长就可以消除贫困,然而真实的情况很难印证这些观点。
对援助进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分配,反映的是不同援助国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法国的援助主要投向它的前殖民地。美国的援助则一直反映其外交政策,在“冷战”期间它支持同盟国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在戴维营协议 [2] 以后则支持埃及和以色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其援助主要投向两国的重建。有些国家会为援助捆绑上附加条件,比如要求援助款必须花在援助商品上(包括粮食援助),或者援助商品需要用援助者自己的船去运输。根据一些估计,美国70%的援助从来没有到达受援国,至少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到达。这种带附加条件式的援助增加了援助国选民对援助的支持,但是也降低了援助对受援助者的效用。近年来,这类捆绑式援助开始大量减少,例如在英国这已属于违法的规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它依然广泛存在。一项最近的估测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捆绑式援助占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的比重(包含粮食援助与技术援助这两个价值较低的项目)已经从80%降到了25%。
与其减贫使命完全矛盾的是,许多政府开发援助甚至不会流向低收入国家,更不要说到达那些穷人生存的国家。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的起点是非常低的。经合组织所认定的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所占有的政府开发援助额度,从1960年的仅1/10增长到了今天的1/3。不过即便是在今天,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政府开发援助流向了中等收入国家。这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糟糕。由于中印两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将中国定位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将印度定位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两国或许都有能力自己解决本国贫困问题。在今日世界,目标贫困人群与目标贫困国家是两回事。
一些政权对提高民众福祉毫无兴趣,也从未在此方面有所行动,但它们仍能获得大量的官方援助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出于政治目的,援助者经常会向它们伸出援助之手。例如,美国曾经长期支持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最近则开始支持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再比如法国一直对其前殖民地予以援助支持,其中就包含实行独裁统治、政府腐败的几个国家。虽然有证据显示转变为民主体制的国家获得的援助大幅增加,但目前仍有大约一半的政府开发援助流向了专制政权。
仅举一个例子。2010年,罗伯特·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所得到的政府开发援助超过其国民收入的10%,若按人均计算,相当于每个人获得了60美元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援助者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鲍尔困境”。如果援助是以那些人们最需要援助的地方为目标,那么,援助多哥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体制,援助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它实际上只会帮助那些独裁者巩固自己的统治,或者让独裁者中饱私囊,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援助可以由不受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管理,但那也至多算是一种补救方法,仍然会有漏洞。因为援助的实际用途是可以被改变的,非政府组织用来建立学校和诊所的资金也可能被当地政府拿走。政府可以用各种名目向非政府组织征税来占有这些援助资金,甚至直接掳走这些钱。比如它们可以向非政府组织进口的货物和设备征税,也可以对非政府组织征收昂贵的运营执照费用。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发生人道主义紧急事件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援助者为了救助军阀统治下的民众,甚至不得不出钱收买这些军阀官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给这些国家送去了粮食,也送去了武器;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的照片被用来吸引援助,然而筹得的钱却有一部分被拿来继续打仗;更有甚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营地也成了施行种族灭绝的民兵组织的培训基地。在援助这件事上,一种是向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提供援助,援助能够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但这些国家又并不急需援助;另一种是向那些治理无能的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在这样的国家,援助能起的作用有限,甚至还有作恶的风险。这两种情况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紧张关系。
以上只是对援助资金如何流动所做的一个简单描述,实际上,富裕国家会在很多方面对贫穷国家施加影响,其作用好坏参半,而援助的确是这些影响之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富裕国家以私人投资方式为贫穷国家提供了发展资本,与世界银行的援助相比,这些资金更为稳定而且也更少受到政治干扰。如此一来,如今的贫穷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对世界银行援助的需求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迫切。另外,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私人资金,如移民给家人的汇款之类,也已经是政府开发援助的两倍。在基础科学方面,那些新发明的药物和疫苗或者基础疾病机理上的新发现几乎都是诞生自富裕国家,而这些新的发明发现的确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福利。手机和网络这些新发明也同样如此。不过与此同时,贸易限制也会阻碍贫穷国家的市场发展,而医药专利保护也可能使贫穷国家难以享受到好的医疗方法。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这种非援助类联系虽然也是有利有弊,但却经常比对外援助要重要很多。这一点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段继续讨论。当然,这不是要否认对外援助在个别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有的国家而言,援助是它们与富国之间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联系。
最初我展开援助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时,以为援助对经济的作用是清楚可见的。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研究也是从援助必然有用这一假设开始的。试想如果我是穷人,你是富人,你对我进行救助,而且是年复一年不断的救助,那最终我肯定不会像当初那样穷困。作为一种直观的判断,很多人以为对外援助的作用也是如此,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所以绝不会想到这种看法有可能是错误的。然而这种本质上也是把援助看成液压流动的直觉判断,确实是错误的。
援助不是人对人的,大部分援助都是政府对政府展开,而且很多援助的目标也并非是为了让人们脱离贫困。我对真实援助体系的简要描述已经说明了以上这样的信息,但是却还没有说明援助的效果如何:在过去的50年里,援助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还是相反?从发展援助委员会和其他地方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援助的数据,同时我们也拥有大量关于经济发展和贫困的信息。不同的国家待遇不同,有一些国家得到的援助会比其他国家的多,此外,各个国家受援助的额度也每年都在变化。我们确信可以依据这些数据发现援助所起到的作用吗?或者更具体地说,那些得到了更多援助的国家(不论是人均所得额度还是受援额度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真的发展得更快吗?当然,减少贫困和经济发展是不同的事情,但无论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才是解决贫困的最为可靠持久的方法。
从前面部分的描述我们就已经清楚知道,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援助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和印度得到的援助和其经济规模相比实在是太少,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却很成功;而一些非洲小国,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得到的援助非常多,但经济发展却难称有起色。相关机构在展开援助的时候希望能对每个国家都有切实的帮助或影响,因此小的国家得到了比大国更多的援助,但是如果援助对经济发展真有那么重要的话,小国就应该发展得更为迅速才对。单从这一点看,援助就是一项彻底的失败。当然,我们不能这么快就下这个结论。人口大国能发展得更快可能源于一些和援助无关的因素,这一点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不过这依然无法正面证明援助能促进一国经济的加速发展。
另一种研究援助有效性的方法是观察在援助过程中得到特别待遇的国家,这包括那些有强殖民关系的国家(比如法国的前殖民地)、因为政治原因而得到额外援助的国家(比如因为戴维营协议而获益的埃及),甚至还有那些在冷战期间被视为“对抗社会主义壁垒”的国家(比如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不用说,这些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有着最差的纪录,原因不言自明。在埃及、多哥和扎伊尔等国,援助并不是用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保障那些得到援助国认可的政权可以继续执政——即使这样做会伤害到这些国家的民众。
有人可能说,那些对腐败和专制政权提供的援助不是我们所讨论的事情,因为它们根本不能算作是发展援助;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了。对这些政权的援助大部分都是以无限制的形式输入到当地的,如果当地政府愿意,这些钱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并且,很多这一类的援助也的确流入了民众有迫切需求的国家。当然,这些例子不能证明,即使援助目标很明确,或者援助对象非常合理,援助也起不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足够清楚地表明,即便对于那些人民急需帮助的国家来说,给予无条件的援助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主意。我想指出的是,即便援助不是给了腐败专制政权,而是给了一些环境更为健康的国家,其所能起到的效用也仍旧是值得怀疑的。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真实援助效果或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在世界上最穷的40个国家里,只有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海地、尼泊尔和东帝汶不在非洲。非洲即使不是穷人的摇篮,也是穷国的摇篮。因此,从过去到现在,有巨量的援助资金流入了非洲;但是,如果援助真的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非洲的经济便早就不该是今天的样子。
图7–1显示的是非洲国家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图中数据以5年为一个间隔,统计时间则从1960年持续到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共有49个国家。从科摩罗群岛、马约特岛到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些非洲国家和地区在规模大小和重要性方面都非常不同,所以取一个简单的平均数并不恰当。因此,我以每个时间段的中位数为准。中位数就是所有数据的中间位置数值,其中一半的国家经济增速高于这个数,另外一半的国家经济增速低于此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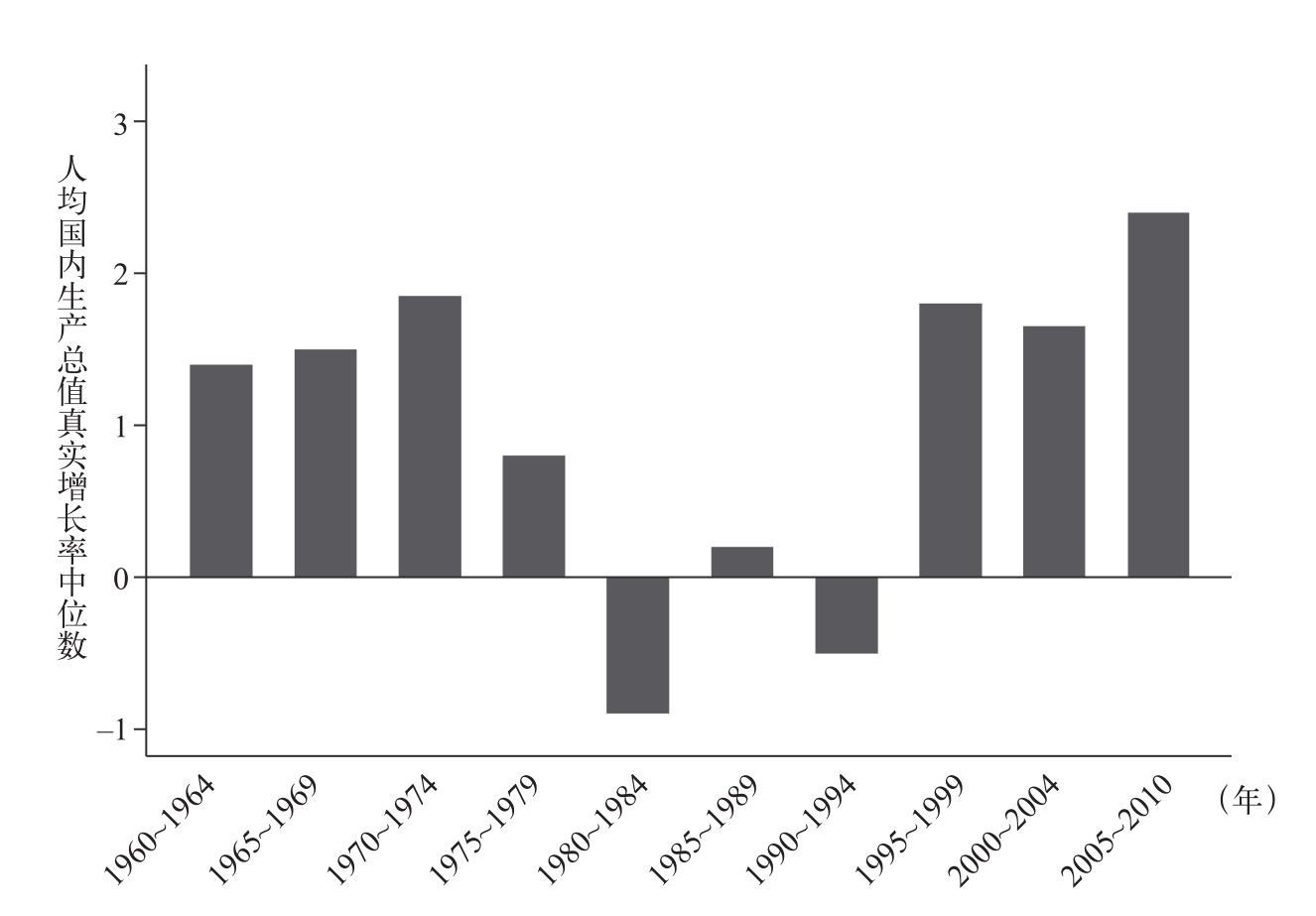
图7–1 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实购买力平价)的增长率中位数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在1%到2%之间;用任何标准来看这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增长,但至少意味着非洲人的生活在逐步改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非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这不但与同时期经济增长很快的亚洲国家相比大为失色,与其自己之前的表现相比,也是一种绝对倒退。以其80年代至90年代的衰败表现看,非洲在独立之后经济低速增长的岁月简直称得上是一个黄金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韩国比加纳富裕3倍,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9。1960年,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肯尼亚的40%,而到了1995年则比肯尼亚高了40%。
1995年之后,非洲的形势有所好转,其经济增长率转负为正;而在2005~2010年,非洲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
这种经济增长—下降—再增长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对外援助带来的变化吗?图7–2显示了非洲人均所得援助额的中位数(以美元计),考虑到非洲较低的物价水平,这些美元的实际作用需要乘以2。图中的这些数字并未根据通胀情况进行调整,若进行物价调整,图的基本走势也将与此类似,只是数据增速会放缓。以购买力计算,在最近几年里,一个处在中位数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居民一年所接受的援助大约等同于100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约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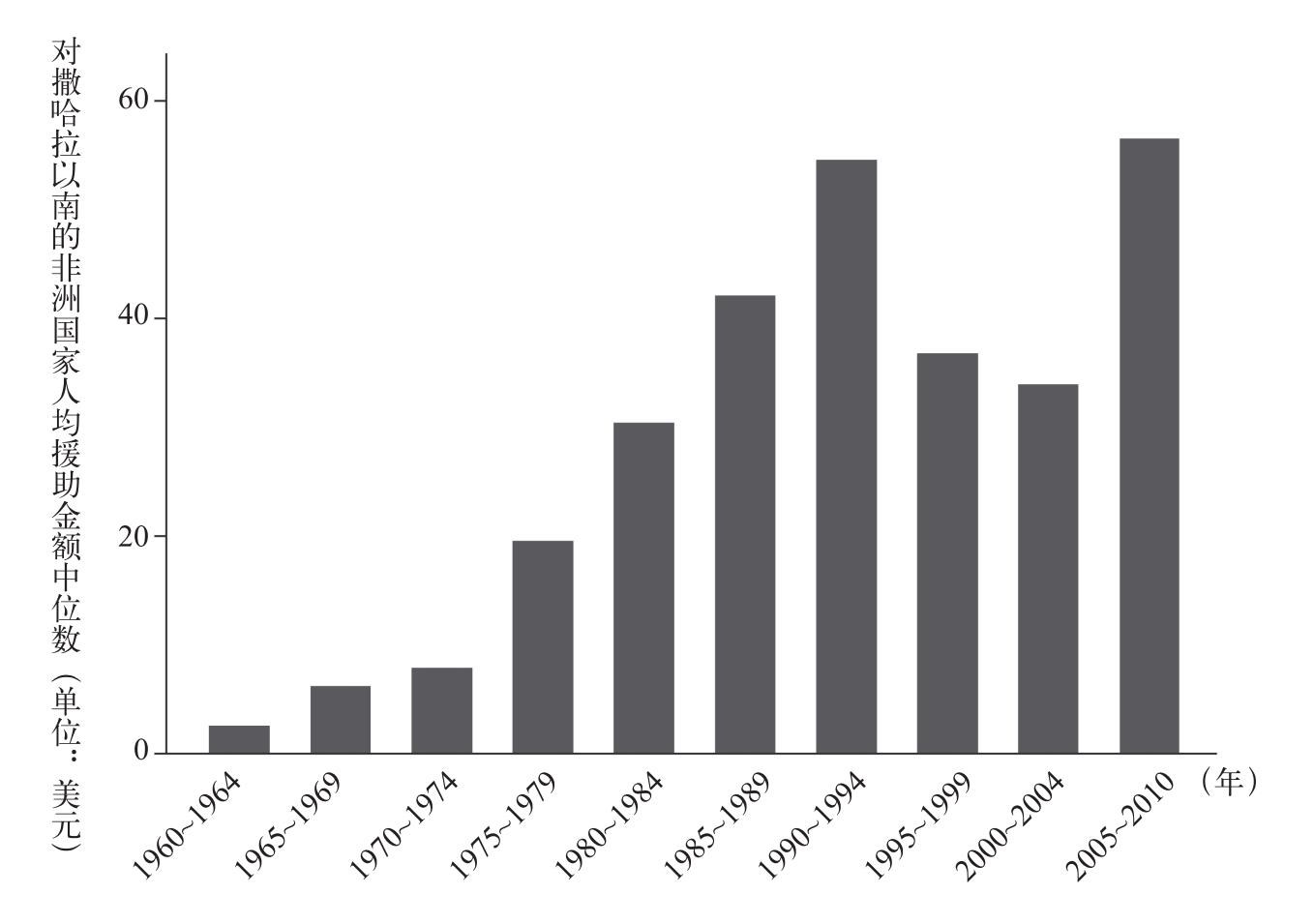
图7–2 对非洲援助金额的人均中位数(以每5年计)
关于援助对非洲经济增长之影响,这两张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其他很多,但这里先有个大致的观点也是自然而然:我们再次注意到,援助看起来的确没起什么正面作用。随着援助金额的持续增长,非洲经济却持续衰退;而当“冷战”结束援助减少时,非洲经济却开始起飞。“冷战”的结束使得向非洲提供援助失去了一个重要理由,而非洲经济却在此时出现反弹。以前有个苦涩的笑话说“冷战结束让非洲迷惘了”,然而这张图却告诉我们,这个苦涩笑话的真正笑点在于“冷战结束竟然让非洲获益了”,而且是因为西方的援助减少了。不过,“冷战结束让非洲获益”这样一个结论对个别的人和国家,比如蒙博托和扎伊尔来讲的确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个一般结论而言则的确是有些过于绝对。
“冷战”终结让援助乐观派认定,当今的援助将不再会被用于反共和扶植独裁者,而是用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强调,现在的援助更具开化作用,所以援助越多,经济增长就会更有前景。这个观点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蒙博托虽然被推翻了,但是另一个专制政府——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政府却在2010年得到了来自美国、英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超过30亿美元的援助。梅莱斯·泽纳维死于2012年,是非洲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之一。埃塞俄比亚大约有4 000万人每天的生活支出在1.25美元以下(其中2 000万人每日生活开支在1美元以下),因此,那些坚信援助可减少贫困的人士一直对埃塞俄比亚青睐有加。梅莱斯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这又让他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好感。美国当然有权去选择它的盟国,但如果其援助只是出于自己国内安全考虑,是为了满足国内选民对贫困国施以援助的呼声要求而不考虑实际的援助效果,那么这种援助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们”。
非洲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基础大宗商品的出口,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这些基础大宗商品多是些未经加工的矿物或者农作物,比如博茨瓦纳出口钻石,南非出口黄金和钻石,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出口石油,尼日尔出口铀,肯尼亚出口咖啡,科特迪瓦和加纳出口可可粉,塞内加尔出口花生。众所周知,基础大宗商品的全球价格一直不稳定,当作物产量减少或者国际需求增加时价格会猛涨,同样,价格剧烈暴跌的情况也经常出现。这些商品价格的起伏涨跌没人能轻易预测。许多非洲国家拥有矿山、矿井和种植园,那些财政上需要依赖对可可粉和咖啡征收出口税的国家,会因为这类商品价格的剧烈震荡而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上不可控的剧烈波动。在本章稍后部分我会就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和对外援助进行对比,现在我强调的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原材料的价格是逐步上涨的,但是从1975年开始,就出现持续下降,不过,石油、铜之类的商品价格在过去的十年再次反弹。由这些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大宗商品出口欣欣向荣之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就必然增长,至少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增长。更多的推导证据也证明,非洲国家收入的增长是对大宗商品市场繁荣的一种反映。
物极必反,1975年以后,大宗商品的价格盛极而衰。私人外国借款对非洲政府的治理失败则推波助澜,世界银行的发展建议也非常失策,因此当大宗商品价格的崩溃来临时,其后果比应当有的更为严重。这样的情况导致这一时期的非洲出现了图7–1中所呈现的经济负增长。“冷战”后非洲经济的增长还有另外一个更富于争议但也具有一定道理的因素,那就是现在的非洲国家拥有比以前更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好政策部分要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性政策调整,同时也是因为非洲拥有了一批训练更为有素的财政官员和中央银行家。如果要评估援助的效果,我们需要把包括商品市场的繁荣和萧条在内的各种其他因素都考虑进去。
大宗商品价格崩溃以后的数年中,非洲经济都表现得很糟糕,但是这一时期对非洲的援助却增长极快。这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在告诉我们,援助的确没有对非洲的经济增长起到作用;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或许说明,正是为了应对贫困,对非洲的援助才出现了增长。事实上,至少有一些新援助是为了让这些国家能够偿还以前的债务,让它们不会违约。当援助伴随着经济的失败而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经济增长和援助之间的负面相关性,人道主义援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如此,援助流向经济增速低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援助的失败,相反这说明援助是成功的,因为援助被用到了它需要的地方。当救生队员救起了即将溺毙的海员时,虽然海员仍旧全身湿漉漉并继续沉浸在刚才的濒死体验中,但我们不能因为其现在的状态大不如落水之前而去责备救生队员。
为了搞清楚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到底如何,研究者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甚至做了很多蠢事。他们将很多同时发生的其他变量纳入研究,并且试图将经济崩溃对援助的反作用考虑在内。将其他因素纳入研究相对简单明了,但即使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援助(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是负相关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决定性的,但不可否认这个结论很重要。我们在研究投资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时,会发现,在机械、工厂、电脑和基础设施以及所有可以支持未来繁荣的事项上,其作用都清晰易见。援助和投资的作用机理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液压流动理论的观点却一直认为,贫穷国家缺乏为未来发展进行投资的资金,而援助正可以补上这个资金缺口。对此我只能再次强调,无论援助能起到什么作用,都不包括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项。
那么如何看待经济崩溃对援助的反作用?可能援助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确有效果,但是这种效果被援助所需要去解决的灾难给抵消了。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几乎无解。虽然许多研究已经尝试做出解答,但是没有一个结论能够让人信服。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这个问题惯常的研究方式。如果能够发现一些国家之所以被援助并不是因为本身存在经济问题,我们就可以排除掉经济衰败对援助作用的影响,进而对援助之于经济发展的效果有一个更为明确的结论。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吗?有,大国得到的援助比小国的要少便可作为例子,相关政治盟国和前殖民地得到的援助更多也可作为例子。但正如我们所见,以这两种角度去看援助,还是得不到援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样一个正面的结论,而且这两种角度本身也很容易遭到质疑。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一个学者都能够给自己的结论找到理由。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统计分析太笼统,因此不会有结果,跨越时间和国家去考察援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肯定不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个人倒是对现存的数据稍有信心,不过对于援助的作用的确更多是抱负面的看法。许多援助者仍旧坚持液压理论的观点,认为应该向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并认为这能够给它们带来更好的未来。但相关数据反驳了这一观点,因为援助和投资不一样,而且私人国际资本可以为贫穷国家所用,所以援助是否有效就无法得到单独的评估。小国以及因政治利益而受到扶持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这也成为援助对经济发展无效的证据。当然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无论是大国的快速发展,还是因政治利益而受到扶持的国家表现糟糕,都可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两个证据仍颇具暗示性。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在那些“不算腐败”的国家援助所产生的效果有所不同,否则我们就不能以很多受援助国非常腐败来作为援助对经济增长无效的理由。这个话题我会在下面继续讨论。
许多人都不是根据援助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去评价援助的,在这一点上内行和外行相差不多。对他们来说,援助就是一些项目:提供资金去建一个学校、一个诊所,或者把援助款项交给那些能提供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组织,以及那些向人们提供艾滋病预防信息及成立小额信贷的组织。在他们眼里,援助可能就是一条能改变一个村庄人生活的公路或者能为数千人带来生计的水坝。包括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内的每一个致力于国际发展的组织都有其成功案例。那些参与者都拥有直接的经验,他们不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效果。他们也会承认失败,不过他们是把失败看作通往整体成功的必要代价。但这样的看法与统计证据所显示出的援助效果甚微甚至有害的结论显然相悖,这是为什么?
一种可能性是非政府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援助所做出的评估过于乐观。批评者指出,非政府组织有强烈的瞒报失败与夸大成功动机,毕竟它们除了分配资金,也同样要去募集资金。批评者也指出了这些评估在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尤其是那些受援助的人要是当初没有获得援助结果会怎样难以评估。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在对援助进行评估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世界银行经常在项目还没有完全结束前就已经做出了对这个项目的评估,因为不断会有压力要求这样的评估早点完成。世界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会定期更换,工作人员则会在各个职位之间轮岗,因此对于世行的人而言,他们更积极去做的是如何把援助的钱派发出去,而不是去证明那些长期项目完成的结果有多好。援助项目最后是否成功与他们的个人职业发展毫无关系,因此,他们也就不会操心如何做出令人信服的效果评估。
这些争议使得如今对援助效果的评估变得更为小心仔细,而随机对照试验(RCT)的方法也常常被重点采用。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判断某个项目是否起作用以及哪些一般规律在起作用的最好方式。(在随机对照试验中,一些人、学校或村庄等会得到援助,而另外的对照组则没有得到援助,所有参与实验的人都是以随机的形式被分到两个组中。)即便之前的项目都经过了认真评估,以随机对照试验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仍然显示,援助的实际作用比之前所评估的要小得多。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世界银行将其所有的项目都予以严格评估,我们就能知道哪些项目有效哪些项目无效,而世界性贫困也可能在很早以前就被消灭。对于非政府组织的那些自我评估,随机对照试验学派,即那些支持随机对照试验的人也总是持怀疑态度。如今,他们已经和那些乐于合作的非政府组织联手,以进一步完善这些组织的评估程序。他们也说服了世界银行在一些工作中运用随机对照试验模式。
判断出某个具体项目是不是成功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之类的一般规律,这样的个别项目试验还很难透露出非常有用的信息。通常来说,试验组和对照组都是非常小的(做试验会很贵),这就导致了结论不够可靠。更为严峻的是,没有理由能表明在某地有效的项目在其他地方仍能有效。即使一个资金援助项目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并且我们肯定这是事实,但援助通常不是单独地在起作用,它需要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加以辅助才会产生效果。面粉可以说是做蛋糕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说,做蛋糕没面粉肯定比有面粉要糟糕,而且我们能用很多试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只有面粉没有膨松剂、鸡蛋和黄油也不行,因为对于制作蛋糕而言,这些辅助的配料也必不可少。
与之类似,教学创新可能会在一个地方的试验中获得成功,然而在其他的村庄或者国家就可能会失败或者不够成功。一个小额信贷计划的成功与否可能得看有多少妇女被组织了起来,也得看男性会给这些妇女多大的自主权。农业教育服务可能会在农民聚居并且可以经常交流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在那些农民分散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服务就可能遭遇失败。如果不能认识到事物的作用机制,就像只知道蛋糕好吃,却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就不可能从某个产生效果的具体项目上发现是什么在起作用。同时,如果对什么在起作用判断错误,其结论也是无益的。如果一种项目或模式复制不是以对作用机制的具体研究为指导,那这样的简单复制就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里会有很多辅助因素的变量存在。因此,当援助机构宣称以它们的方式运营的项目非常成功,而整个世界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须明白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消灭全球贫困的真正答案。
还有一种可能性:资金援助的项目很成功,而援助本身却是失败的。即便存在一个理想的援助机构,它只会在某个项目通过了严格的评估之后才提供资金,这样的援助也同样可能失败。首先,很多的项目在试验时非常棒,但是真正实施时却未必如此,这样的情况非常令人恼火但是的确经常发生。产品模型与制成品是不能等同的。在现实中,政策是由真实的官僚所执行,出自他们手中的政策效果不可能和学者及世行工作人员所设计的一样完美。同时在现实中也会出现很多在评估中始料未及的事情。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是,援助资金导致的某些私人服务的增加会削弱政府对同一种服务的供应。即便政府的产前护理体系不是很好,即便护士和医生经常怠工缺勤,那些非政府组织所运营的诊所也需要从其中招聘医护人员,并且通过高薪挖角,它们会逐步将公共医疗系统的资源掏空。如此一来,援助的净效益也就低于没有考虑这方面问题时所做出的评估。另一个被广泛争论的例子是对大坝作用的评估,因为我们很难对大坝建设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鉴别。
以试点项目来评估某些新的理念经常是有益的,然而当项目规模扩大后,其结果往往会与试点结果有所不同。一个教育项目或许可以帮助人们从高中或者大学毕业,然后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很多贫穷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属于最为人所青睐的职业。但是如果这样的项目扩展至所有人,而政府的规模并没有相应扩张,那么这样的项目就没有带来净效益,至少以到政府就业这一指标来看是如此。农业援助项目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个农民可以因为援助而提高生产率,但是如果所有的农民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原本是对一个人有利的事情,最终可能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几乎所有涉及农业、企业或者贸易的援助项目在进行独立测试时都不会有问题,但一旦规模扩大,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个援助项目可能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当其规模被扩大至全国范围时,就可能遭遇失败。完美的项目评估与全国整体上的援助失败并不矛盾。
援助机构经常会给那些本已顾此失彼的政府带来沉重的行政负担。政府机构不得不批准援助项目;不得不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监控;不得不与在其国内工作的大量国外机构进行会面商谈。很多贫穷国家缺乏行政与监管能力,这些都限制了其国家的发展与减贫进程。本身意在助人的援助项目,却使得当地政府官员无法专注于更重要的任务,并对成功发展所需的国家能力造成了破坏,这绝对是一种讽刺。援助让政府的时间与精力转向了对外援助机构而疏忽了本国公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国家越小,一个政府越无能,以及援助的金额越巨大,这样的政府转向就可能产生越为严重的后果。
认真仔细地评估援助项目,搞清一个项目是否实现了其最初目标,尝试寻找也适合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大力肯定的工作。一个成功的令人信服的评估,可以发现让资金发挥作用的确切机构或领域以改善民众的生活,尽管这样的结论常常只适用于某个地区而难以一般化,其作用仍值得肯定。但是,项目评估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有用什么无用这样的一般规律。那些成功的项目评估也不能保证现实的援助就一定会有效,因为从根本上说,对援助的效果判断需要从整体的经济情况出发,它不是以某些具体的项目为准,也不是要去区分项目的好坏。在谈论项目的评估时,一定要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援助这件事,一定要思考援助给一个国家带去的整体后果。
要理解援助如何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援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会繁荣与经济增长需要相应的环境,而政治与法律制度在环境的建设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援助,尤其是大量的对外援助,会影响这些制度的运行与变迁。政治经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而且在援助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政治制度就有了优劣之分。对外援助的大量流入,使得地方的政治生态变得更为恶劣,同时,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制度体系也遭到了援助的破坏。援助还会削弱民主和公民的社会参与,除了经济增长受到影响,这是又一个直接损失。援助有很多正面作用,比如它让那些原本将会失学的儿童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那些本可能逝去的生命也因为援助而得以幸存。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援助的正面作用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权衡对比。
发展经济学将“二战”之后开始的经济增长与贫困下降视作技术问题,这一派的经济学家总是向我们解释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及其统治者是如何给民众带去繁荣的。即便也曾对政治的影响有所思考,这些发展经济学家们依然认为,出于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政治家会扮演一个民众保护者的角色。而政治本身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公民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以及管理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根本没进入这些学者的视野。这些发展经济学家也没有认识到政府在其运转之中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在一种长远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扮演一种可信的伙伴角色。对发展经济学这种看法的反对意见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直到近几年,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政治体制等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开始关注政治政策本身。
如果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达成某种形式的契约,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出现。政府要想维护领土完整,保持对暴力机关的垄断,或者仅仅是为了建立法律体系、维护公共安全、保证国防安全以及提供其他公共产品,就需要具备相应的财力。而要想具备这样的财力,政府就需要从被统治者身上抽税。正因为政府需要税收,而如果没有纳税人的参与整个征税过程就难以完成,所以政府在需要得到约束的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对政府使用纳税人资金实施的一些项目进行评估,可以直接反映出选民对政府表现的满意程度。这样的反映方式在民主政体中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因为政府在方方面面都有筹集资金的需要,这就常常对执政者造成一种约束,使得他们需要关注纳税人的诉求或者至少是其中某一部分人的诉求。人们对大规模资金援助最为强烈的反对理由之一,是认为援助会削弱政府在筹资方面所受到的约束,因为一旦约束被削弱,政府就无须民众同意也能实现资金筹集,而在极限情况下,它还使得本应普惠人民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一种有害人民的体制。
在富裕国家,政府保护公民理所应当,而在贫穷国家,如果税收能力不足,国家就会拒绝向公民提供更多保护。法院不作为或者官员腐败,人民就得不到法律保护,警察也不再保护民众,甚至可能骚扰与剥削穷困百姓。债务无法偿还,契约难以履行,或者政府公务员屡屡索贿,这些都可能导致业务无法正常进行。人民还会面对来自匪帮和军阀的暴力威胁。本地特有的致命病虫害本来是可以预防的,然而它们仍可能会威胁民众尤其是孩子的健康。人们可能会用不上电,无法上学,或者得不到完善的医疗服务。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地区来说,若具有以上的这些风险意味着此地可能仍然处在贫困之中。所有的这些风险都会导致贫困,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国家能力的缺失。任何破坏国家能力的事项,都与改善穷人的生活这一目标格格不入。
认为援助会威胁制度体制的这种观点认为,援助的破坏性取决于援助额度的大小。中国、印度以及南非近年来所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数额一直低于它们国民收入的0.5%,并只是偶尔占到政府支出的1%以上。在这些国家,援助并没有对政府的行为或者体制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在非洲,情况就大不相同。在将近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9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所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占到了其国民收入的至少10%。
如果考虑到政府开发援助主要流入了当地政府手中,非洲这些国家所接受的援助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就更高了。在贝宁、布基纳法索、民主刚果、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多哥和乌干达等国,它们接受的援助占其政府近几年运行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5%。在肯尼亚和赞比亚,政府开发援助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4和1/2。由于多数的政府支出都是提前设定并且在短期内无法更改,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自由支配支出几乎全部都是依靠国外的援助。稍后我们就会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援助者就能够左右政府的支出分配,事实绝非如此。但是,援助的存在和援助的规模的确从根本上影响了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行为。
执政者无须协商认可便可自由支配的东西并非只有援助一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便是另外一种。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19世纪中叶的非洲。当时世界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对棉花的需求十分强劲,而棉花的主要来源,一是美国南部,另一个就是埃及。那时候埃及与外部世界最为主要的贸易品种就是棉花。当时的埃及统治者,即被后人称为“现代埃及奠基人”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以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价格从埃及的农民手中收购棉花,然后转手出口到海外,他和他的宫廷因此变得富甲一方。美国内战的爆发使得全球棉花的价格3年时间翻了3倍,与此同时,在阿里帕夏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帕夏治下的埃及,也被不久之后的一篇英国报道形容为“极尽奢华”:在埃及,“巨额的资金被投入公共工程与生产性的工程,这种投入是东方式的,不是进展过快就是方向错误。”而这其中,就包括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但是,这种资金支出的规模过于巨大,因此即便是战时的棉花价格也无法支持其进行下去,于是伊斯梅尔就到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借款。而当战争结束,棉花价格也出现崩盘,埃及境内随之出现了叛乱与军事入侵事件,最终埃及被英国占领。
棉花的价格在1853年是每112磅9美元,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4美元,1865年则飙升至33.25美元的高点,然后在1870年回落至15.75美元。有人会说,即便伊斯梅尔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外国的借款人也早就应该知道会有这样的麻烦出现;但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是一样的,借款人可以指望另一个新政府,即英国来保护和恢复他们在埃及的投资。当然,这样一个悲剧故事也不是没有光明的一面——无论怎么说苏伊士运河都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其所带来的收益绝对不能忽视。
大宗商品价格猛涨和对外援助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现金的进进出出完全与国内需求和国内政治脱节。棉花价格的大幅上涨是由美国的内战所引起的;而援助的决定因素,则或是援助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或是“冷战”之类的国际事件,抑或是反恐战争之类。援助的增加会刺激政府支出,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而在埃及的事例中,我们也看到政府在花钱时完全无须咨询民众或者获得他们的同意。只要矿业国营,价格上涨,而且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足,统治者即便没有民众的认可也能维持统治。而即便没有矿石这样的天然资源,充足的对外援助照样可以让统治者高枕无忧。扎伊尔的蒙博托就是一个例子。国外的援助被拿来维持蒙博托政权的统治,并且大量的资金被源源不断地消耗在这上面,最终,当这个政权垮台的时候,那些存在瑞士银行账户或者其他地方的援助款也被糟蹋得所剩无几。当然,有人会认为蒙博托政权之所以得到支持要归结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而其他的援助则需要受援国政府对援助国负责,因此,援助者会把这些受援助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现实当中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援助者的意愿所起到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很多。
跟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一样,援助还会对当地的制度体制造成其他不良的影响。如果没有无限制的资本流入,政府就需要征税以维持运行,但是要征税就需要先得到纳税人的支持。中东很多石油生产国的民主发展不健全,部分要归因于石油所带来的巨额收入。非洲国家多数实行总统制,因此那些得到外部资金援助的总统就可以依靠资助或者军事镇压来维系国家管理。在这样的国家,议会权力受到限制,总统也极少会询问它的意见;无论是议会还是司法机构都无法限制总统的权力。这些国家不存在对权力的制衡。在极端情况下,援助或者大宗商品出售所带来的大量外部资金流入还会增加内战的风险。这是因为有了外部资金撑腰,统治者就会拒绝分享权力,但与此同时国内对立两方也会为了争夺这些资金而大打出手。
为何对援助者负责不能代替对当地民众负责?如果统治者拒绝咨询议会,放弃对腐败的警察机构的改革,或者用援助资金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援助者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援助?一个原因是,援助政府及其选民——真正的援助者,无法实地体验援助的真实效果,因此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便是危机出现,援助者最终了解到了发生的一切,停止援助也并不是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即便是受援国极为恶劣地违背了最初的援助协议,即便援助国曾经非常想早点结束援助,但最终援助仍然不会被停掉。
那些用援助资金建设的项目到底如何,只有当地民众有直接的体验,也只有他们能做出判断,而援助者做不到这一点。对援助效果的判断不可能总是非常准确,关于因与果,关于政府某些具体行为的价值,国内总会有不同的声音;但这些都是正常的观点分歧,是可以通过政治程序来调和的。但是,援助国或者不生活在受援国的选民却没有这样的体验与判断。他们不掌握关于援助成果的直接信息,必须倚仗负责分配援助的机构的报告来做出判断,也正因此他们的关注点是在援助的数额而不是效果上。反过来,那些援助机构也因此只对真正的援助者负责,即便受援者出了问题,他们也不会负责任,因为没有相应的机制。我曾经询问一位在一家著名非政府援助机构工作的官员:“你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没想到这位官员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非洲,而是美国西海岸,而这里正是这家援助机构几个最大的出资人居住生活的地方。我们之前提到过,对于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而言,当他们原本负责的项目终于有了看得见的效果之时,他们本人早已经被调去负责其他的事情了。所以,援助者根本不会对受援助的人们负责。
有时候,援助机构也知道援助出了问题,会被他们亲眼见到的事实所震惊,但是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一位国家援助机构的主管曾经向我讲过援助资金是如何落到一帮杀人的匪帮手里的。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匪帮已经进行过一次屠杀行动,如今又继续接受训练和武装,以便再次进行此类行动。我问这位主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给他们提供援助?他回答说,因为援助国的国民觉得进行援助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会接受援助别人就是伤害别人的这种说法。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尽量减少援助所造成的各种伤害。
虽然援助者很清楚哪些援助的限制条款是必须遵守的,但他们还是不乐意处罚那些不遵守相关限制条款的受援国政府。援助者经常会威胁受援国:必须好好表现,否则就惩罚你。但是当这个国家真的表现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们又不愿意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一旦采取行动,将有可能伤害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选民。对于那些会杀人的武装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如果受援国的情况没有这么糟糕的话,他们的确可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援助限制条款存在“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时间不一致性是经济学家钟爱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在事前想要做的事情,在事后并非一个最符合利益的选择。那些接受援助的政府对此了如指掌;他们清楚援助者的底牌,因此敢将这些事先的援助限制条款全然不放在眼中。
那又为何不去强力执行这些援助限制条款?
1992年,经济学家拉维·坎布尔担任世界银行驻加纳的代表。当时,加纳政府违反了此前的协议,擅自给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加薪80%,于是坎布尔按照要求准备执行援助限制条款:冻结一笔之前已经答应发放的贷款。这比款项数额巨大,几乎相当于加纳进口额度的1/8。但这样的举措遭到了包括加纳政府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反对。若贷款取消,很多无辜的人肯定会受到伤害。加纳人不用说,那些外国的承包商也会因此拿不到工程款。更为重要的是,援助者与政府之间原本正常良好的关系也会因此中断,这不仅对政府有害,也伤害到了整个援助行业的运营。“援助者的援助资金关系千头万绪,一旦援助被停掉,尤其是突然被停掉,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坎布尔说。实际上,援助行业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配援助资金,这个行业的人主要就是靠分配援助资金以及维持与受援助国家间的关系为生。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共同妥协,面子保住了,而贷款照常发放。
肯尼亚的例子则展现了援助者、受援国首脑以及议会之间的关系。援助者时常被该国首脑及其亲信的种种腐败行为激怒而停掉援助。这时候,该国首脑就不得不召集议会,并就政府该如何提高收入以保证职责履行进行商讨。对此,援助者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因为知道如果援助停止,他们就会受到不再被需要的威胁,于是只得恢复援助。而政府这边,任务完成议会就会被解散,直到下次需要的时候再次组建。然后,那些受援国的部长大臣们会长长松一口气,之后拿着援助的钱去订购德国最新型号的奔驰汽车。在当地,人们把这帮依靠援助大发其财的人称为“奔驰一族”。
1984~2005年间,毛里塔尼亚总统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可谓是在这方面最会见风使舵的人才。为了获得援助,他转向亲西方立场,并于1991年放弃了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他在国内镇压人民的行为还是惹怒了援助者,导致所有的援助被取消。但这位总统很快又有了绝妙新招:他宣布毛里塔尼亚承认以色列,从而使毛里塔尼亚成了最早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然后他又宣布进行政治改革。援助因此再次对其开放,然而当这位总统拿到援助之后,毛里塔尼亚的这些所谓改革就立马停止了。
援助国的国内政策也常常让援助易开难停。那些充满善意但是显然又不了解内情的国内选民,会给政府内的援助机构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对全球贫困“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那些机构的援助人员确实知道自己在好心办坏事,却依然难以停掉援助。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政客对此情况都了然于胸。于是,受援国的政府会将本国的那些贫困民众作为“从援助者那里榨取钱财的人质”。塞拉利昂是这方面一个最为恶劣的例子。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塞拉利昂再次定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并保证给予其新一年的援助之时,该国政府官员竟然开派对大肆庆贺。
另外,当援助国的政客因为某些不相关的原因丧失支持率时,他们也会采用开展对外援助这种手段为自己捞取政治美誉;即便援助明显是在被滥用,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也会反对结束援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非洲的穷人们就成了西方政客沽名钓誉的牺牲品。2001年,英国给当时正值选举的肯尼亚提供了援助,而这些钱都用在了破坏选举以及维护一帮贪腐之辈的统治上。林登·约翰逊曾对一场几乎不存在的印度饥荒大肆宣扬,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对“越战”的关注,更是为了从美国农民手里购买粮食,从而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援助者和受援者即两个国家的政府,在背弃自己民众这方面结成了同盟。对民众的榨取从未消失,自殖民时代以来唯一发生了改变的,只是被榨取内容的性质。
还有一些现实的原因,也限制了援助者执行援助限制条款。援助项目是可变更的,受援者可以表面承诺把援助用于医疗,但实际上把钱挪用到很多未经许可的项目上。对于援助者而言,要想监督这样的挪用行为通常非常困难。援助行业本身也充满竞争,如果这个国家拒绝提供援助,另外的国家就会立即补进来,而其援助的限制条款也会有所不同。那些想要执行限制条款的援助者会因此被挡在门外,而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对受援国家的政治影响以及相关的商业机会,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
近年来援助机构试图改变以设定限制条款作为援助条件的做法,转而希望和贫穷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受援国根据自身需求提出受援计划,而援助国决定该如何予以资助,然而事情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富裕国家的援助政府仍然需要对其选民负责;而受援国对此了如指掌,所以在规划自己的受援计划时,也会从援助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过程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腹语表演”。在一方拥有资金而另一方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到底怎样的伙伴关系才能长久地保持下去。
政治和政客以其惯有的方式破坏了援助的效用,反之,援助也会破坏政治的作用。很多事情本应是受援者自己拿主意,但都被援助者代表了;即便援助国政治民主,但也不应该替非洲决定是抗艾重要还是产前护理重要。为援助设定限制条款侵犯了一国的主权。如果一个资金雄厚的瑞士援助机构跑到华盛顿对美国政府说,“只要你们废除死刑并让同性婚姻完全合法,那么我就会帮助你们还清所有债务并且为老年人医疗保险出资50年”,美国政府会同意吗?若是有哪些国家的政府认为这样的政策对本国国民无害,那也太不正常了。让另外的国家来干预一国政治,绝不能使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契约关系。想要从某个国家的外部来促进此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目前仍然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让人们相信,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增长。同样,援助对于民主制度或者其他制度的影响也很难被证实。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发现,很多小国实际上拿到了大量的援助,但是政治却变得越来越不民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又是接受援助最多的地区。那些从其前殖民者身上获得援助的国家,也并非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地方。最为有趣的是一项与图7–1和图7–2相对应的发现:自“冷战”之后对非援助减少以来,非洲不但出现了经济上的增长,民主程度也大幅提升。与其他的情况一样,出现这样的结果自然还有其他可能的因素,但是如果对外援助的确会对民主有破坏作用,那么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可预期的了。
援助者曾长期认为,援助与经济发展本身都只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样的观念反而加重了对外援助的反民主作用。依照液压流动理论(我们只是在修水管子),在对方真正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争论。这样的观念使得援助者和顾问们对地方政治愈加忽视或者不耐烦。人口控制就是一个最恶劣的例子。很明显,对于援助者而言,如果人口总数更少,则每个人得到的援助就会更多,生活也会变得更好,但是对于受援国而言,相反的情况才是千真万确。西方所倡导的人口控制经常需要非民主政府或者那些得到很多援助实惠的政府协助才能开展,而把援助资金用于人口控制,则是援助会产生反民主并压迫民主效果的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他国在良好意图掩盖下的专制只能靠有效民主这剂药来解。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的《反政治机器》一书是援助与经济发展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弗格森在书中阐述道,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在非洲的莱索托援助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发展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却对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极深的误解——现实中,那里是可以为南非矿业发展提供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地方,然而外人却将这里假想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自给农业经济。如此一来,那些照着这种假想而设计的农业投资项目,自然也就如同在月亮上搞花草种植一样,不可能成功。执政党操控了这些项目,将其变成了实现自己政治目的同时打击对手的工具,而那些忙着修理水管的项目管理者却对此一无所知。结果,发展没有出现,贫困也未减少,唯一的效果是当地政权对政治的垄断控制进一步增强了,而那些靠榨取而存活的精英分子对民众也更加漠视。
发展型援助的技术解决方案一直在变化。最初,工业化、战略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点,继而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健康与教育被重视,直到最近重心又重新回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但即便如此,对于发展援助的主流看法仍旧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主导这些项目的人,对这样的看法几乎仍无任何的怀疑与自省;而第一世界国家中政治潮流的风云变幻,似乎也没有动摇“援助是技术性的”这一定论。在林登·约翰逊担任美国总统时,世界银行的口号是“与贫困作战”,而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口号就变成了“理顺价格”。在美国内部,这样的政治变化思路非常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然而对于受援国,我们的思路就完全错误了。
毫无疑问,援助和资金援助项目成就了很多事情;正因为有了援助,道路、大坝以及诊所才会在这些受援国出现。但是,援助的负面作用也一直在那里;即便是在良好的环境中,援助也会损害制度、伤害地方政治、破坏民主。如果说贫困和不发达是体制落后的主要后果,那么大规模的援助流入实际上会进一步削弱体制或阻碍发展,这与其最初目标背道而驰。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尽管援助经常带来一些直接的正面影响,对援助的统计却没有显示出其能带来任何整体性的正面作用。
通过对外援助来减少全球贫困与一个国家内部对穷人的救济截然不同。许多人反对福利救济,在他们看来,对穷人的救济只会鼓励穷人的行为方式,对贫困有固化作用。但全球援助与减贫的逻辑并不在此。关于对外援助的讨论,其焦点并不在于它们对全世界的穷人贡献几何(实际上的确没什么贡献),而是在于其对穷国政府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外援助之所以会让贫困状况恶化,是因为它会导致受援政府更加漠视穷人的需求,从而给穷人带来伤害。
即便援助存在正面影响,其负面作用还是带来了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哲学家莱夫·韦纳对彼得·辛格的看法(我在本章开头部分有提到)持有批评意见,他说,“救助贫困可不是从池塘里拉上来一个溺水的孩子”。辛格的比喻是没有意义的。那些赞成给予穷国更多援助的人需要解释清楚,援助为什么要受到政治约束,他们也应当认真思考援助和之前的殖民主义到底有何相同与不同。如今我们都把殖民主义看成是坏东西,因为它牺牲了别人使我们自己受益,而把援助看成是好东西,因为这是牺牲我们(尽管非常轻微)而帮助了别人。但是这样的理解太过肤浅,也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种自我陶醉。其实当年殖民主义的口号也是帮助别人,并号称是为那些尚未充分开化的群体带去文明与启蒙,而这或许只是对抢夺与剥削的一种掩盖而已。《联合国宪章》那慷慨激昂与鼓舞人心的序言是由曾任南非总理的扬·史末资所写,史末资当时将联合国视为保存大英帝国与白人“文明”的最有力希望。当然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即后来很多国家脱离了殖民主义,然而这些国家的新领导者,除了出生地和肤色之外,其本质与之前的白人殖民者并没有任何区别。
时至今日,倘若人道主义的言辞还只是政治家收买人心的口号,而援助也只是为了体现我们在减贫方面的道德责任感,我们需要自问:这么做有没有伤害到那些受援助的人?如果我们正在做伤害他们的事,那么援助就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在帮助“他们”。
外部援助拯救了贫穷国家千百万人的生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为千百万儿童送去了抗生素和疫苗,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因此而下降。对携带病菌生物的控制与消灭,让不少曾经的危机之地成为安全之区。在国际间的合作努力之下,天花被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消灭也近在咫尺。援助机构为上千万的儿童提供了口服补液疗法;每年疟疾会夺走100万非洲儿童的性命,如今援助机构也在为他们提供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以使他们远离这种疾病的侵扰。1974~2002年,在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努力之下,河盲症这种曾经在非洲肆虐的公共健康疾病也已接近被全部消灭。
近年来,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被投入到了艾滋病的治疗中,当然在这方面,非洲仍然是最主要的受援国。截至2010年年底,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这一疗法无法治愈艾滋病,但可以保住患者性命)的艾滋病患者已经从2003年的不到百万人增加至1 000万人。抗艾滋、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是这方面最主要的援助组织,而这个组织的最大出资人是美国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前者主要是以多边形式为各国的艾滋病防治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是通过双边方式为美国认定的那些最急需援助的项目提供援助。除此之外,这些机构也积极推动有关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的研究,比如它们尝试使用抗逆转录药物来预防病毒传播与感染。此外,男性包皮环切手术对于预防艾滋病的作用也得到了论证。对于艾滋病,目前仍无有效的预防疫苗,但是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之中。犬儒主义者会说,如果不是美国人也遭受到了艾滋病的侵扰,美国恐怕不会这么投入地去做艾滋病的相关研究。这种对于动机的质疑,抹杀不了美国在这上面所取得的成就。
如果这就是全部,那援助在健康提升方面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当看到别人濒临死亡,而我们又无须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可以施以援手时,我们的道德责任感会特别强烈。伸出援手,只不过是一个文明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我们自己早已经摆脱了这样的苦境,现在所做的,不过是要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同样早日免除死亡的危险。
当然,我们知道仍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孩子可能只是因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死于那些原本不至于致命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痢疾,还有营养不良之类,但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应该为此提供更多的援助。而健康水平的提高,或许就是援助想要达到的一个总体目标。修建道路、浇筑大坝、搭建桥梁,这些扶助工程对人们生活的改善作用往往难以清晰衡量,而“理顺价格”或者是政府财政体系的修正之类,其效用更难评估。与这些相比,拯救人的生命的确是一个更为清晰的目标,也更容易量化计算。不过,前面所说的这些类型的援助肯定也同健康援助一样发挥了作用,只不过不易觉察而已。此外,我们之前所言及的“援助会造成政治腐化”可能也有夸大之嫌,或者相比于援助的种种益处,政治腐化只是付出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代价。
但是,就健康方面而言,援助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与现在所起到的作用相比,援助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很难有清晰的论断。而如今所取得的成就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只不过是目前来看,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全球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多数是得益于一系列成功的健康援助计划,我们将它们称为垂直卫生项目。这些项目由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上而下地推行,并且也得到了地方卫生当局的配合,同时还会招募一些地方卫生人员参与其中。早期的一些疫苗接种就属于此类项目,而像控制蚊虫防治疟疾这样的杀虫行动,包括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行动也属于此列。不过,对艾滋病的防控则与此不同,虽然为了治疗艾滋病经常需要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但要推动抗逆转录药物的使用,就需要地方医疗机构与当地医疗卫生人员的大规模介入。
还有一些项目,比如“单病种项目”以及“疾病专门项目”等,与垂直项目的说法有重合部分,不过,这些项目不仅仅是指那些旨在消除某种疾病的卫生项目,也可以用来指代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以及抗艾滋、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这样的项目。这些垂直项目或者疾病专门项目与那些水平项目或者地方性医疗保障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所指的不仅仅是那些提供日常医疗服务的医生、诊所以及医院机构,还包括很多的公共卫生举措,比如提供洁净的水源、良好的卫生设施、基本用药、健康所需的营养以及对地方性流行病的防控等。垂直项目的成功往往伴随着水平项目的失败,而后者最主要的失败,通常就是不能构建一个完善的基本医疗体系。举世闻名的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就强调“人人享有健康”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基本的医疗保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贫穷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援助组织都被要求加强对基本医疗的物质和技术支持。对于那些期望得到非垂直型健康援助的国家,这个宣言仍然是它们高举的一面旗帜。
要实现基本医疗保障,需要的是一个有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垂直项目。垂直项目可以靠“从天而降”直接输送,但基本医疗保障依靠这种方式是无法实现的。实际上,垂直项目有时候甚至会阻碍地方医疗体系的建设,比如,垂直项目需要抽调护士和护理人员,使得他们脱离日常岗位。这些人原本从事产前护理工作或者疫苗接种工作,而现在却要被派往遥远的乡村去跟踪刚爆发的脊髓灰质炎。日常医疗体系的建设和维护都非常复杂,不仅在穷国是这样,在富裕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建设这样的医疗体系需要相当的国家能力,而这是很多贫穷国家所欠缺的。这提醒我们,援助与受援国的国家能力经常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是,如果援助想要帮助穷国解决目前所存在的健康问题,并拯救那些因为“生错地方”而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那么健康援助就不能再仅仅是针对某种疾病的援助。不过,这里存在一个与之前类似的问题:穷国的这些困难,真的是依靠国外的资金就能解决的吗?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对本国基本医疗的建设花费投入甚少,甚至,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迪翁·菲尔默、杰弗里·哈默和兰特·普里切特的说法,这些政府“用于健康卫生的公共预算,基本上都被公立医院拿走了。通过高昂的公共支出所培养出来的医生用昂贵的医疗手段为城市精英服务,而在同一国家,却有孩子因为花不起很少的钱看病或者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而死”。那些腐败的官员经常把本该用于健康卫生的资金掳走,而这却极少引起公众的激愤情绪。以上的三位学者就举了一个例子:一家报纸曾经指控当地卫生部挪用了500亿美元的外部援助资金,这个卫生部竟对该报纸提出强烈抗议,声称这家报纸应该去搞清楚,挪用已经是经年累月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海伦·爱泼斯坦曾经写过在乌干达流传的一个笑话:有两种艾滋病,分别是肥艾滋病和瘦艾滋病——“那些得了瘦艾滋病的人,会变得越来越骨瘦如柴,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肥艾滋病则会让负责发展事务的官僚、外国顾问以及医疗专家等遭受折磨:他们要前往各种富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参加奢华的会议和研讨会,还要拿高工资,于是就变得越来越胖了”。缺乏基本医疗资金与对医疗支出的贪腐是贫穷国家经常同时出现的两大现象。
在不少国家,用于医疗的公共支出已经少得无法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医疗需要,而这通常会让人们觉得,要弥补医疗的这一资金缺口,对外援助将必不可少。医疗支出太少的确常常千真万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医疗体系上投入更多就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单纯扩张医疗系统往往只是带来更多非正常营业的诊所、更多挪占援助的官员以及更多只拿钱不干活的医疗工作者。
即便垂直项目对于促进“人人享有健康”没有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即便大量健康援助资金的流入和其他的援助一样带来了各种各样不曾预想到的副作用,但是,只要对生命的拯救确实有帮助,我们就应该把这种援助继续进行下去。而不管是想通过公共部门还是管理良好的私人部门来实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要实现这样的服务的前提是拥有一个有相当能力的国家或政府,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医疗服务都无法直接通过对外援助实现;而这是那些收入处在最低水平的国家所不具备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那些能力不具备的国家就不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健康医疗措施。比如,低收入国家也能提供一些传统的公共健康产品,像安全水源、基本的卫生设施,以及害虫防治等。虽然要提供这些产品也并非易事,但是这些国家有相对足够的理由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至少私人部门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健康产品,而对于政府而言,相对于建立一个个人医疗体系,这些事情看起来也似乎简单易行。
我们之所以要开展援助方面的努力,或许是因为觉得应当为此做些什么,又或许是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在提醒我们,必须为此做些事情。但是,这种援助驱动力恐怕恰恰是错误的,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一部分,而绝非提供解决方案的开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是谁将我们摆到了这样的位置?我在本章从头到尾想表达的观点是,对于穷人的需要及期待,以及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行,我们拥有的常常仅是极为贫乏的理解,这导致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以我为主,简单轻率,对受援者造成的伤害往往大于对其的帮助。只要我们行动,就几乎一定会出现负面的意外后果。而即便出现了失败,我们也会固守己见坚持不改:因为这是“我们”的援助产业,我们有大量的职业人口依靠这个产业生存,而援助更能为我们的政治家带来名望与选票,如果不把援助进行下去,以上所有的事业都会陷入危险之中。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但贫穷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那些已经在富裕国家被证明有效的事情。这些已经富强起来的国家,以其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与独有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下实现了发展。没有任何人给过它们援助,也没有任何人为它们出钱让它们去推行维护出资人利益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保证没有挡住这些贫穷国家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让贫穷国家自我发展,不予干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不要再做那些阻碍它们发展的事情了。走出贫困的先行者已经告诉后来者,实现摆脱贫困的大逃亡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有相应的方法。即便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些逃离贫困的方法很多(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可行的。
与初衷极为矛盾的援助就是我们所做的阻碍贫穷国家发展的事情之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国外的援助规模巨大,这不但破坏了当地的体制制度,也熄灭了它们的长期繁荣之火。为了建立反共或者反恐联盟,很多的对外援助被用来维系当地的榨取型政客或政治制度的统治。这样带附加条件的援助只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让贫穷国家的普通人遭到剥削和伤害。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并假装是在帮助他们,令他们更加雪上加霜。来自外国的大量援助,足以瓦解腐蚀那些本可能对人民有益的政治家和政治制度。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再问我们应该做什么,同时需要帮助那些富裕国家的公民认识到援助可能有益,但也可能造成伤害。不考虑援助资金是在作恶还是行善就规定将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或者0.75%用于对外援助,是极其荒谬的。正是这种盲目的目标设定导致了国家纷争与生灵涂炭,大使们不得不去谈判协调促使战争停火,而援助管理者的职业内容,也从帮助别人发展变成了为别人抚平创伤。
援助远非富裕国家在穷国摆脱贫困道路上所设置的唯一路障。通过贸易、协议,以及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起了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机构以及国际事务间的种种规则,都对穷国的富强之路有深刻的影响。我会在后面阐述这个问题。
援助的支持者经常会对一些反对意见做出让步,但却辩称,虽然在过去援助没有起到效果,有时候甚至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未来将可以甚至一定能做得更好。他们坚信,援助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更为有效,而且援助的实施可以避开以前的种种陷阱。在过去,这样的说法也经常会进入我的耳朵,这就像一个酒鬼老对我说,“再喝一杯,以后就再也不喝了”。这些说法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援助之外的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可行方法,就像要戒除酒瘾,除了依靠自觉之外,还有很多有效的方法。
认为援助需要更有智慧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我们认为没有了世界银行或者英国国际发展署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或者认为最好的援助就是没有援助,但现实却是援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可以关闭所有的国际或国家援助机构,也不能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关停。既然如此,如何让援助富有智慧?
经济学家、联合国顾问杰弗里·萨克斯长期坚持认为,问题不在援助太多,而是太少。萨克斯推崇我所说的液压流动式的援助方式,即先找出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比如农业问题、基建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健康问题,然后算出每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少钱,最后进行合计。以此方式最后得出的总额,要比现如今援助的真实数额高出很多倍。如果萨克斯的方法是正确的,则做成一件事,所有相关的问题也必须都马上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们几十年前的所谓“大推动” [3] 方法。而如果想要解决全部问题,援助的规模就必须扩大。但是,历史显示,现今这些进入富裕行列的国家并没有依靠任何形式的大推动,更不需要从外部而来的大推动。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以萨克斯思想为指导,联合国所推行的千禧村项目就比同国家其他的村庄发展得更好。为液压流动式的援助所忽略的就是我所说的:这样的援助资金会瓦解当地的政治体制,使得当地的发展更为艰难,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仅依靠一张家居建材超市的购物清单,哪怕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从一个国家的外部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帮上什么忙。
提供更好的援助这一理念在《巴黎宣言》中得到了体现。该文件由111个国家和26个多边组织于2005年签署。《巴黎宣言》就像一份新年的愿望清单,其中列举了很多想要实现的目标,比如实现合作、维护受援助国的自主权、提供高质量的援助结果评估、明确责任,以及增进援助预测性等。这份宣言的实质意义当然也和新年愿望差不多。换个比喻就是,这份宣言像是为一个病人列了一份如何才能健康的清单,却对他为什么生病以及该如何进行治疗只字不提。在这一章中我们早已提到,合作关系的失败、责任归属的不明确、国家自主权的丧失以及对援助结果评价的失效等,都深深植根于援助的现实之中。当所有的资金都只属于合作的一方时,真正的伙伴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当所有的责任都归于那些心地善良但不明真相的外国人时,受援助国家不可能有自主权。实现美好愿望这一类事情,写进宣言非常容易,但是那些与援助所面临的政治现实不符的善意,很难对援助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
如果援助的提供能够附带一些限制条款,或许能起到更好的作用。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坎布尔担任世界银行驻加纳代表时的所见所闻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即便受援助者背信弃义,援助者也很难或者无法停止援助的发放。并且一个援助者停止了援助,随时还会有其他的援助者出现,这些新的援助者或对于政策善恶的理解不同,或无心干涉受援国的内部事务。不过,由于整个的援助产业最终还是要对富裕国家的援助者负责,所以这些新的援助者也必然会提出某种形式的限制条款。但这些限制条款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是问题所在。
一种办法是让受援国的政府承诺会在未来实行普惠大众的德政,然后再让这些国家成为援助的候选者。这便是通常所说的遴选机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限制条款的一种。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运行机制与此类似。受援国家需要先展现其善意,然后援助者才会提供合作机会,然后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遴选机制会让那些维系压迫统治的国家政府拿不到援助,但是如果一个被选中的政权在受到援助后还是偏离了正义的轨道(援助本身经常会导致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就又回到了是不是要停止援助的两难之中。
遴选机制的致命弱点是它会将很多最为需要援助的国家排除在外——比如那些当政者完全漠视民众福利的国家。对于视提供援助为道德责任的人而言,对这些人提供援助是最为紧要的。在那些民众有强烈援助责任感的国家(美国不在此列),民众的压力使得援助机构几乎没有可能忽略那些生活在德政失败的国家中的人们。在有德政的国家,贫困问题完全可以依靠本地力量解决,而几乎无须外部援助;在无德政的国家,外部援助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当地的政权照样可以像盘剥当地人民一样将这些非政府组织榨干。
另外一种办法来自全球发展中心(CGD)。该中心是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掌握着关于经济发展的大量信息,同时在援助改进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全球发展中心的主席南希·伯索尔以及健康经济学家威廉·萨维多夫提出了一种他们称为“货到付款”的援助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援助者和受援助国家会首先制定一系列双方都认可的目标,比如在一个给定的时间之内为80%的儿童接种疫苗,或者在5年之内,将婴儿出生死亡率降低2%,或者实现干净水源的提供等,等到这些目标都实现之时,援助者再拨付援助资金。不过这一方法的支持者已经察觉到,货到付款式的援助会使得穷国业已脆弱的评估系统更加雪上加霜,同时也可能会刺激受援国在各项目标数字上作假。并且,很多的目标并非全然能为受援国政府所控制,比如恶劣的气候会影响分娩,突发流行病会增加婴儿的死亡率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照常给予援助,那么援助本身的激励作用就打了折扣,而如果援助者缺乏弹性不对各种意外酌情考量,受援国的政府就可能不会为了一项自己本身支付不起而做了又可能得不到补偿的政策去冒险。
货到付款式的援助也不能解决我们熟知的那种有德政权与无德政权之间的进退两难。那些发展态势良好的国家,根本就不需要我们鼓励去从事一些它们不想干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优先目标与它们的优先目标一致,那么就无须我们给予援助;而如果双方之间的优先目标不一致,则把我们所认定的优先事项强加到它们头上是不道德的。想想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瑞士援助机构会资助美国政府,前提是美国要取消死刑以及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种强加就是不道德的。而对于那些榨取型和压迫型的政府而言,用钱收买它们或许会有作用——它们会像盘剥自己的民众那样,很高兴地从我们身上榨取资源。只要能拿到援助,它们乐见自己的百姓被伤害。这种与恶魔打交道的事情本来也可以忍受,但现实情况是援助机构为了能够被允许为这些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要为它们提供武器,即援助资金被用来武装那些过去杀过人未来还要杀人的暴徒,而只有这样援助机构才能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人的家人。这就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在戈马所发生的真实事情。
大规模的援助不能产生效果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有效果,而那些想要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一直在围绕着同样的基本问题一遍又一遍打转。桥修起来了,学校也建起来了,药物和疫苗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负面作用却始终存在。
当援助资金减少时,以非洲国家为主的部分国家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这些国家,对外援助占据了它们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同时几乎相当于其政府支出的全部额度。援助国的国民加强对援助问题的重视是极为重要的,那种认为给予金钱就能消灭贫困的观点看起来逻辑清楚,事实上是明显错误的。援助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主要是因为援助错觉的存在,而援助国内部的政治压力,也使得对援助制度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那些具有奉献精神与道德情操的援助国民众,实际上是让受援国那些本就陷入困境的人们雪上加霜,这是援助所造成的一大悲剧。
也有一些例子能说明援助是有益处的,或者至少能证明援助是利弊两平衡。健康方面的援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的领域也存在。例如,在一些政府表现较好的国家,援助只占其经济总额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府,突破各种困难与障碍最终没有变成外来援助的俘虏,把这些援助用在了当地的合理发展目标之上。
经常有人问我:援助多少才算多?应该把援助减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如何知道应该在哪里停止援助?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提问,因为这里不存在一个“我们”的问题,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对援助喊停的超国家机构。就目前而言,最为紧急的任务是停下那些业已展开的援助,并且让富裕国家的人民知道,大量援助有害,而且援助越多越有害。我们应让他们了解,不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是帮助世界上穷人的最好方法。那么,如果想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并且切实减少援助,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以便卸去身上的援助责任?
援助的种种问题,多是源于其在受援国内造成的种种意外。如果我们能置身事外,远离这些国家,或许很多意外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曾指出:“我们很难想象,大量增加的援助会在非洲本土得到有效使用,把更多的资金投在其他领域,则有可能会为非洲带来更有成效的帮助。”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基础知识,比如对细菌致病理论的掌握,对高产种子品种的发掘,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知,对疫苗作用的认识,以及对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了解等,都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和接受援助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没有毒副作用。
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等某些创新的救助方法出现,也不能等着富裕国家有自身需求了再采取救助行动。对那些已不再威胁富裕国家但仍伤害贫穷国家人民的疾病,比如提供疟疾等的防治药物和手段,就是一种新型的对外援助。现如今,富裕国家的医药公司通常是靠药物销售来收回其研发的投入。依靠当前的药物专利保护,它们通常可以将药物高价出售给病人或者病人的保险公司以及政府。但是,贫穷国家的病人们难以支付这些处于专利保护期的高价药品,在商业利益的压力之下,富裕国家的政府也会通过制定国际规则,使得贫穷国家无法突破专利保护的限制。这些规则属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范畴,尽管对这些规则的遵从并不符合贫穷国家的利益,但只有遵从这些规则,贫穷国家才能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医药公司声称知识产权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保护。与穷国居高不下的药物价格相比,穷国的制药商会不会无成本仿制它们的药品然后再将其卖回富裕国家,是这些制药公司更为担心的事情。
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大约10年前这些药物还只存在于富裕国家的时候,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高昂的药物价格经常会引发争论。但现在我们看到,虽然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已经被认真地对待。如今,全球获得抗逆转录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超过了1 000万人并仍在持续增加。对于艾滋病之外的一些疾病,比如第三章表3–1所列举的一些致死疾病,相关的治疗药物多数都已经超出了专利保护期,因此价格便宜很容易购买。除了关于艾滋病的治疗药物之外,药物的价格并不是主要问题。
缺乏有效的疫苗或者药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疟疾或者肺结核这样的疾病在富裕国家已经极不常见,市场对这类药物的潜在需求已经非常低,因此,制药企业也就没有研发相关治疗药物的动力。一方面是穷国还有需求,另一方面是只有富国的药企才能生产相关药物,两者之间无法衔接。因为缺乏生产动力,新的技术也就无法在正确的方向上得到运用。如果援助者可以通过援助提升穷人的购买力,为制药企业创造出研发动力,那么新的治疗药物就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哲学家托马斯·博格提出了一个他称为“健康影响力基金”的方案:如果制药企业为人们带来了健康福音,那么这个基金就会按照贡献比例对该企业予以奖励。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许能够解决药价高以及制药企业无动力研发新药的问题,从而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低价获取各种新老药品,而制药企业也可以从该基金获得资金奖励。这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宏伟计划,它的巨大优点在于可以让制药企业抱着最大限度造福全球人类健康的目标来选择它们要攻克的疾病难题。但这里也存在一个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的问题:我们很难将健康水平的提升归结于某一具体类型或领域的创新,更不要说是某一种具体的新药物。尽管所有的数据都摆在那里,对于疫苗和新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起到的作用,医学史家仍然争论不休。我们对全球多数地方的人口死亡率和发病率数据掌握得并不完整,而即使所掌握的数据非常齐全,我们也不能确切说明健康改进或者恶化的原因。而没有相关的数据,我们也很难对每家制药公司应该得到多少资金奖励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
另外还有一个预先市场承诺方案,所谓预先市场承诺,是指政府与国际机构结成联盟,同意以一个预先设定的价格向制药企业订购某种具有指定属性的新药物。相对而言,这种方案的野心较小,但是却更为具体可行,预先的承诺会让制药企业产生研发药物的动力。目前,肺炎球菌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已经取得了成功。肺炎球菌每年会造成全球50万儿童的死亡,但如今有十个国家的儿童因为此承诺而获得了对肺炎球菌的免疫。该疫苗的主要资助者是加拿大、意大利以及英国,其次是挪威、俄罗斯以及盖茨基金会。该计划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Alliance)运营,在该联盟网站上,我们可以查找到相关制药商的详细资料,同时,该计划对于制药商和援助者的各项规定也登在该网站上。
援助不见得非要提供贷款,提供建议也是一种形式。对于世界银行而言,现有的结构导致它很难提供除了贷款以外的实质性技术援助,而贷款实质上只是为援助出钱。因此,贫穷国家对于技术知识的渴求,单靠世界银行很难满足。尽管随机对照试验并不是一种能正确认识事物运行原理的方法,也不能简单将以此得到的结论复制使用,但是那种认为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应该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实践真知的观点则是正确的。一个政府想修建一座大坝或者考虑将供水系统私有化,就会想要知道那些走过类似道路的政府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仅是最终大致的效果,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谁会因项目受益谁会受损,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当然,世界银行和其他援助机构的经验也并非总是可靠,很多事件都证明它们非常自大无知。
国际组织亦可以通过国际谈判,尤其是贸易协议的方式来增加穷国的国力。美国和其他的富裕国家会同贫穷国家展开双边贸易谈判,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缺乏代理律师或专家,这类谈判往往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则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当然,这也并非易事。例如,如果世界银行的建议会给美国制药业所认可的某些意向造成实质性的阻碍,美国政府则几乎肯定会对世界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施加压力。不难理解,若想让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美国容忍其相关政策和决定,世界银行就不能动真格地去帮助穷人。虽然这听起来太过愤世嫉俗,但全球贫困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决,其中很多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障碍。
援助并非发展的唯一障碍。对于富裕世界的国家而言,只要有人付钱,它们就十分乐意为其提供武器装备。我们也总是很急切地要与那些明显对发展民众福祉毫无兴趣的政权结识,开展贸易,甚至借贷给它们。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不少的应对建议。比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和希玛·贾雅昌卓安就呼吁对那些“恶”政权进行国际贷款方面的制裁。一旦某个政权被认定是恶的,则那些为这个恶政权提供贷款的组织或机构将无法通过国际法庭向其继承政权追讨欠款。这样的措施会切断对恶政权的贷款,或至少让贷款流向恶政权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国际社会也会降低从这类政权国家购买石油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的意愿,即便还是要从这些国家购买相关产品,在何时购买以及什么前提下购买方面也会变得更为透明。在美国,最新的金融改革已经要求石油、天然气、采矿业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其与各国政府之间的交易记录。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仍需要进行全面的协调,很多没有签署相关协议的国家,仍旧会从这些恶政权手中购买大宗商品以供自用,或进行再出口。
富裕国家的贸易限制常常会伤害穷国农民的利益。在非洲,农业活动吸收了将近3/4的就业人口,但与此同时,富裕国家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来补贴自己的农民。以糖和棉花为例,富裕国家对本国生产者的补贴压低了这两种商品的全球价格,同时也让穷困国家的农民失去了以此谋生的机会,富裕国家自己的消费者也因此利益受损。这种情况的存在,证实了组织严密的少数人的确在用政治权力对抗大众的利益。如果穷国是食品等农业产品的纯进口国,那么富裕国家的补贴措施降低了食品的全球价格水平,将可以使得穷人受益。但美国的生物燃料补贴却因为消耗了大量的农产品以及其他资源,因此对穷人有害。如果国际社会能够联合行动起来限制或者消除此类有害的补贴政策,则必将有助于消除全球贫困。
移民对减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成功从穷国移民到富国的人生活得以改善,而他们寄回祖国的钱即海外汇款也可以帮助自己的家人提高生活水平。海外汇款的作用和援助所起到的作用大不相同,它可以让人们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有可能改善当地的各项治理情况而非产生破坏作用。但与自由贸易的问题相比,移民的问题更加棘手,即便在那些扶助外来人口呼声最为强烈的国家也是如此。为外来人口尤其是非洲籍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提供奖学金,以便让他们可以在西方短期停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法。如果运气好,这些学生不需要依靠援助机构或者国内政权就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便今后不会返回祖国,这些离散各地的非洲人也是一种丰富的资源,可以为其祖国的项目发展提供帮助。
援助不能降低全球贫困,但以上种种策略却有此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富裕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代价甚至零代价来实施这些策略,其中的某些策略要比另外一些在政治上更为灵活可行,而诸如预先市场承诺这样的措施,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实行。所有的这些策略都不会像流向穷国的援助那样产生无数的后续问题。当普林斯顿的学生们过来对我说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更富饶的地方时,我总愿意这样劝告他们——不要想着把自己未来收入的多少多少捐出去,也不要老想着雄辩地劝服别人增加对外援助;而要去影响自己的政府或者自己去政府工作,让这些政府不再施行伤害穷人的政策。我们要支持各项国际政策,以使全球化更有利于穷人,而不是对穷人造成伤害。在我看来,要帮助那些仍未挣脱贫困的穷人实现大逃亡,这将是最好的方法。
[1] 千年发展目标: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全体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一项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物价水平为标准)的行动计划。——编者注
[2] 戴维营协议:该协议于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是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一项原则性协议。——编者注
[3] 大推动,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模型,主要认为要想为工业产出创造市场,必须推动所有的工业同步发展。——译者注
未来将会怎样?
我在本书中所讲到的大逃亡是一个有着正面结局的故事。通过这场大逃亡,亿万人口逃离了死亡与贫困。尽管不平等仍然存在,尽管仍有千百万人未能逃离死亡与贫困之苦,但这个世界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世界。当然,在“大逃亡”这个比喻的出处——电影《大逃亡》那里,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在电影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成功逃出,大部分逃狱者最终又被抓了回去,更有50人被处决而死。电影如此,我们如何确信我们的大逃亡结局会截然不同?
未来,或许仍有众多不确定,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憧憬未来。
在我们之前的诸多文明大都毁灭于某些强力,所以我们的后代绝不能认为,我们这次就可以成为例外。在欧洲和北美,我们已经渐渐将“明天会更好”当成了一种必然。诚然,在过去的250年中,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与以往人类历史中一些文明持续的时间相比,250年只是白驹过隙,那些曾长久存在过的文明也曾经以为自己会永存于世,最终却都消失了。
现在有很多威胁足以毁灭我们,气候变化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但直到如今,关于气候变化也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可行的明确解决方案。私欲可以战胜公共需求,这一点在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他发现,是对树木的盲目砍伐导致了复活节岛文明的最终毁灭,而他所思考的是,那个砍掉岛上最后一棵树的人,当时到底在想些什么?
战争并未停止,政治的危机无处不在。
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为人类带来了物质生活与健康水平的持续进步。但是,如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科学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攻击。很多宗教极端主义者都握有政治权势,而且也获得了那些利益遭到科学知识威胁的群体的支持。
科学不能让人完全免于疾病,新的传染病随时都会出现。最厉害的病种会引发一部分人的死亡,然后力量耗尽,再回到它们的动物宿主身上。但是,艾滋病的大流行警示我们,任何可怕的结果都会出现,艾滋病绝对不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虽然艾滋病导致了3 500万人死亡,是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我们还是很迅速地确认了病毒并研发出相关的治疗处方。未来,比艾滋病更难确认更难治疗的疾病很可能还会出现。如今,全球的医疗系统都普遍使用抗生素,然而,由于农业上的滥用和抗药性的进化,抗生素的作用也受到了威胁。在与细菌的斗争中,我们目前所取得的胜利绝非最终的胜利,这场斗争更像是一场持久战,双方会各有胜负。现阶段我们是占了上风,但这只是战争中的一个阶段,而并非战斗结束的尾声。进化会伴随人类活动而进行,细菌终会发起对人类的反击。
经济增长是人类能够逃离贫困与物质匮乏的动力所在,但是如今,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履蹒跚,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几乎各地都出现了不平等扩大的现象。比如美国,当前公民收入与财富的极端不平等是过去一百多年未曾发生过的。财富的急剧集中会损害民主和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造性破坏也会受到压制。这种财富的不平等让跑在前面的人截断了落后者追赶的道路。
曼瑟尔·奥尔森曾预测,日渐扩大的主要既得利益群体会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逐自身利益,而这样的寻租行为将会导致富裕国家的衰落。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将使得分配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必然会侵害到另一方的利益。很容易想象,当经济增长迟缓之时,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华尔街与主街之间、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以及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之间,将利益冲突不断。
但尽管有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仍然对人类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人类逃离苦难追求幸福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绝非轻易就会被挫败。未来的逃亡者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前面的人会把后面的路堵死,但是开山辟路的知识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无法阻止知识的传播。
经济增速放缓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统计者遗漏了很多关于质量提升的统计,尤其是服务方面,它在国家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却未得到很好的计算。信息革命以及相关的工具设备等,也为人类福祉做出了很多贡献,然而却无法量化统计。这些领域或技术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愉悦,无法反映到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中,只能说明统计方式本身不完善,而不能说是技术或其为我们带来的愉悦不够。
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不发达国家,因此对他们而言,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实上,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超过25亿的人口,近年来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即便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然而在未来几年,“后发优势”将仍足以保证它们保持一个超出平均水平的经济追赶速度。
非洲国家面临着无数可能性。一些非洲国家避开了过去由自己造成的灾难,经济治理水平大幅改善。如果西非能够摆脱对援助的过分依赖,并停止破坏非洲的政局,则本地驱动下的发展也大有希望。另外,我们也需要让非洲人的天分得到自由发挥。
虽然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在下降,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死亡人口正在转向老年人,而延长老年人的寿命,并不像拯救儿童生命那样可以极大提高整体人口预期寿命。另外需要重申,问题的核心是找到合理的评估标准,而非具体去评估什么。要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变好,预期寿命并非总是正确指标,没有任何理由说延长中老年人的寿命没有拯救儿童的生命有意义。
虽然人类健康仍然受到威胁,但是人们的健康水平也在大幅提升。在过去的40年里,人们在对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有迹象显示,我们在癌症的治疗方面也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如果足够幸运,人类将有可能在癌症治疗上复制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健康水平最终会提升的终极原因是,人们在这方面有诉求,同时对于健康水平提升所需的基础科学研究、行为研究、药物研发、治疗疗程研究以及治疗设备的研制等,做好了随时埋单的准备。当然,创新不能通过购买而得,也不是有需求就会有创新,但是毫无疑问,有需求又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肯定就会有相应产出。
虽然艾滋病大流行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它成功说明,新的基础知识和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对需求做出反馈,而且这种反馈可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尽管对于那些死于艾滋病的人而言,这种反应速度还是太慢,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对艾滋病的反应速度已经是相当快了。这说明科技的确在发挥作用。
还有很多正在发生的进步,没有在这本书中得到讨论。譬如,暴力在减少,今天,人们被谋杀的概率已经大大低于从前;与50年前相比,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实现,一个社会集团镇压另一个集团的事情已不常见,并且在变得越来越少;同时,与之前相比,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大为增加;另外,全世界的人都长得更高大了,而且也似乎变得更聪明了。
在世界上的多数地区,教育受重视的程度在提高。如今,全世界80%的人口都受过教育,而在1950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文盲。在印度以前的部分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未接受过教育,但是现在她们的女儿几乎全部进入了学校。
期盼以上所谈论的诸多问题可以在世界各地同时取得进步,或者取得持续进展是不现实的。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新的人类逃亡也会和以前一样带来新的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一切困难与挫折,都在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解决。所以,我期望,眼前的这一切挫折与艰难,也都将在未来被战胜和解决。

从个人感情到政治、商业,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塑造了新的常规和新的预期,从而使人类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以文明的、社会的方式行事了。我们无法做出长期的承诺。对所有不能直接或立即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和观点,我们越来越难以产生兴趣,我们甚至无法容忍这样的人和观点。我们的同理心弱化了,我们越来越难以相信人类之间有任何共同点,而一旦这种信念崩溃,民主制度也将随之面临挑战。
献给林恩、莫莉、马修和
我的老邻居安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长江学者、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
孙子曰:“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就是说决策者如果因为一时感情的冲动而做出判断,多半要丧师辱国。这句古训翻译成民间老百姓的俗话,就是那句著名的小品金句——“冲动是魔鬼”。可见,冲动对个人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那么,冲动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记者保罗·罗伯茨的著作对此做出了回答。
全书洋洋洒洒30余万字,从“冲动”这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代美国经济演化、社会变迁与政治沿革的切片。这位在美国著作颇丰、多次获奖的资深记者和畅销书作家给读者们描绘的美国是这样的:企业不顾长期社会成本,无耻地追求最快的回报;政治领导人条件反射性地选择短期解决方案,而不是广泛、可持续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案;在这里,人们感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市场所利用,这个市场痴迷于人们的私人欲望,却忽略了人类的精神幸福或家庭和社区的更大需求。
上述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罗伯茨给出的答案是“市场和自我的虚拟融合”。换言之,就是快速发展的技术、腐败的意识形态和商业道德底线结合在一起,将美国社会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
显然,罗伯茨所描述的美国,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的“美国印象”大相径庭。但细细品来,似乎一切也都在情理之中。尤其是联系最近四五年来美国社会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以及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罗伯茨的深刻洞见似乎为我们对当代美国的经验感知提供了理论上的诠释。这正是这本书吸引我将它一口气读完的主要原因。
在书中,罗伯茨坦言:
“我们的经济产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个人商品(从智能手机到金融创新产品,再到神奇的保健药品),却不再能产出足够多的公共产品(比如公路、桥梁、教育和科技、预防性的医药产品和清洁能源)。这些公共产品对经济的长期稳定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公共产品的缺乏已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能制造出等离子电视机、座位加热器、牙齿美白产品以及能一步一步指引你到达最近的潮流酒吧的手机导航软件。但当我们需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金融体制改革、医疗体制弊病或者现实世界中的其他重大问题时,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这段直白的叙述让一个已经高度“异化”的“发达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顽疾毫发毕现而又鲜血淋漓地摆在每一个读者面前,并迫使我们去思考: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到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从事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到现在也将近40年了。但说实话,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来的美国,即使是我也感到非常陌生。现在的美国和我青年时期见到的美国,好像真的是两个国家。这种困惑促使我不断思考美国社会、政治变迁背后的动力与逻辑究竟是什么。
在最近几年的讲座和文章中,我多次提到自由主义的流行可能是造成美国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与罗伯茨的观察不谋而合。自由主义在哲学中也可以被称作“个体主义”,就是从个体的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府的关系。这种思想发展出的经济学就会强调私人企业,并认为自发形成的市场最有效率。而在政治上,个体主义哲学认为政府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带来问题,所以主张小政府,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在文化层面,这种哲学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
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是社会性的。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有了很大提升,人类个体相对于自然和他人都变得比以前安全。因此,英国就出现了现代自由主义,然后风靡了整个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人类进步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危机。贫富分化与政治一结合导致了世界大战。所以,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资本主义,让社会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经济效率下降了。
20世纪70年代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标志就是1979年的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资本、服务于资本。在我看来,它对美国社会造成了破坏。支撑美国的有三大力量:资本、政府和民众。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的力量变得非常大,造成了这三者的失衡,酝酿了许多矛盾。
我们不妨把当代美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做一个类比,这样中国读者们可能更容易理解这本书中的美国社会变迁。古代封建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期循环。一般来说,新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都很小、很能干,也相对比较清廉,豪强的力量也很少。这个时候,社会治理起来比较容易,税收不重,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但是,随着王朝变得稳定,一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豪强,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就拿不到他们的税收。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到了后期也会越来越臃肿,效率下降,对社会税收要求也随之变高。这时候,社会就面对着两股压迫的力量,一个是庞大的政府,另一个就是豪强。民众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起义,将它们全部摧毁,再重新建立一套。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美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困难。现在美国的华尔街、大资本就相当于古代中国的豪强。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府也已经变得很庞大臃肿了。所以民众越来越困苦,矛盾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了解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不断嬗变的对外政策,也包括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在性格上就很不一样,以前的美国是很有远见的、愿意承担责任的,比较宽容大度,也很有幽默感。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焦虑、冲动的美国。
现在,美国人民以微弱的优势选出了拜登做总统,这或许也是一种自我纠偏吧。作为建制派的代表,拜登和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能否消弭过去4年来美国一系列非常行为给美国国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中美关系、美欧关系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同时,中国人民也要有信心、有战略定力,因为美国的对外行为也不是它一家说了算的,同样取决于国际互动,尤其是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换言之,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客观上也有帮助美国人民纠偏的功效。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作者即便通篇痛心疾首、针砭时弊,目睹美国困境加剧而“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但他仍不忘给他的美国读者指出光明之所在,坚持认为美国社会还有能够发现希望的迹象。他尤其为当下一些普通美国人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底线价值观所进行的反抗鼓与呼。这样的拳拳爱国之心不仅让我深受感动,更引起我的深思:一个在高度“异化”的“发达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内浸淫多年的记者,尚能以如此清醒的头脑针砭时弊、恳切直言,同时又“不忘初心”,总想着为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指出一条向善、向着光明、回到真实而持久的美好世界的道路,那么我们呢?面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好时代,又怎能不擦亮初心、奋发向前呢?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与读者诸君共勉。
是为序。
赵向阳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如果您只想浅浅地了解一下美国为什么会相对衰落,我建议您读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美国真相》(从经济学和制度理论的视角进行剖析),或者旅美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许倬云说美国》(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结合个人生活经验来解读美国),但是,如果您想深入研究美国的“病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推荐阅读《冲动的美国》。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记者,该书作者保罗·罗伯茨对问题的分析深度和渊博的知识储备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学者,《冲动的美国》读来令人感到震惊,或者感到汗颜。相比其他同主题的作品,这部作品基于一种更加底层的逻辑,也就是心理学的视角,他把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了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之后)消费主义的兴起(或者准确地说,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者相伴而生)。商家处心积虑地贩卖焦虑,诱惑消费者即时满足、过度消费,这导致自我和市场过度融合,甚至被市场吞噬。美国人民放弃了曾经持有的那种建设性的、可持续的价值观(以生产为中心、长期导向、“我们”高于“我”等),而采用一种短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单纯强调效率、客户满意度、创新无止境而摒弃了传统价值的可取之处、股东价值最大化等)。
从个人心理到消费者行为,从企业经营到宏观经济,从宏观经济到政治制度,从国内政治到全球局势,罗伯茨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分析严密,读来非常“烧脑”,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反复咀嚼,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今天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以调和的政党纷争、民意撕裂、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等,可以说都是冲动消费的直接或者间接产物。从政治上看,美国各个党派放弃了对长期政治目标的承诺(比如,美国国内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不接受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等),转而选择暂时性的、收益率最高的党派主义的策略,以迎合愚蠢而短视的选民。而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和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家更是如此,他们相互勾结,以创新之名推波助澜,激发人们的欲望,堪称火中取栗。美国甚至世界,已经被他们推向了失控的境况,很少有人再拥有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
反观中国,我们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与美国相似的困境,让人感到非常悲观。但相比之下,中国有强大的政府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或许可以超越这种短视和即时满足,采取一致性的集体行动,解决重大而长远的问题,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没有完全失控的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阅读《冲动的美国》不是要幸灾乐祸,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
在西雅图以东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坐落着美国第一座帮患者戒除“技术毒瘾”的康复中心。这所康复中心的名字叫作“重新开始”。这里距离微软、亚马逊及其他数字革命时代的支柱公司的总部并不远,然而这条蜿蜒的乡间小路却仿佛引领我们走向一扇不为人知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我们即将迎来的更广阔世界的全貌。这间康复中心的大部分患者正试图戒除网游。这些患者都曾出现强迫性网游成瘾的症状,而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未来的幸福指数。对不熟悉这个世界的人来说,这种成瘾现象也许很难理解,但当你倾听过这些患者的故事,你就会慢慢理解他们的感受。在一间能够眺望草坪的起居室中,29岁的布雷特·沃克讲述了他与网游《魔兽世界》的故事。《魔兽世界》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角色扮演网游,这款游戏为玩家塑造出一个蒸汽朋克的中世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玩家将扮演战士等角色。在过去的4年中,虽然游戏把沃克的现实生活搞得一塌糊涂,但他在网络世界中拥有着近乎完美的身份:他在《魔兽世界》中拥有无限的权力,并有着黑帮大佬和摇滚明星般的地位。沃克说:“在游戏世界里,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当他这么对我说的时候,我感受到沃克的语气中混杂着骄傲和自嘲。沃克说:“那个世界是我的避风港和天堂。”
其实沃克自己也理解这种具有讽刺性的情况。沃克花了无数时间扮演网络游戏中的超级英雄,而在现实生活中,网游成瘾使他身体虚弱、一贫如洗,并且在社交上极度孤立——在最严重的时候,沃克甚至几乎不能与人面对面地谈话。事实上,这还不是网游成瘾最深层的效应。有研究显示,高强度、长时间地进行网络游戏活动会改变人类的大脑结构,影响大脑负责决策和自我控制的部分。网游成瘾的这种效果与毒品和酒精的效果类似。网游成瘾会导致患者的感情发展推迟或异常,使患者认为自己无能、脆弱,无法参与社交,也就是自我凌驾于超我之上。用“重新开始”康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网络成瘾治疗专家希拉里·凯什的话说:“这些患者完全被他们的冲动控制。”
这些特点导致网游成瘾者更容易受到网络世界复杂魅力的吸引。游戏公司当然希望游戏玩家玩得越久越好:玩家玩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升级游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游戏设计者开发了复杂的数据回馈系统,尽可能刺激游戏玩家升级的欲望。随着玩家在虚拟世界中不断前进,他们向游戏公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而游戏公司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把后续的游戏设计得更加逼真。也就是说,玩家玩得越久,游戏公司得到的数据就越多,玩家后续的游戏体验也就越逼真、越吸引人,这样的循环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魔兽世界》会定期发布升级程序,又称“补丁”,补丁为玩家提供新的武器和技能。要想在《魔兽世界》中继续保有上帝般的权力,玩家就必须使用这些新的武器和技能,因此升级对玩家来说总是有致命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永动机般的循环。这种永无止境的循环既受游戏公司对利润的贪婪所驱动,又是游戏玩家永远无法满足的自我表达欲望所导致的。在彻底放弃《魔兽世界》之前,沃克从不拒绝任何升级的机会。只要有可能取得任何一点额外的权力,沃克都会选择立刻获得这种权力,即使这种游戏世界的权力在不断侵蚀他的现实生活。
从表面上来看,沃克的故事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并不会整天沉溺在游戏世界的虚拟战争之中。事实上,这种电子时代的弊病显示的是后工业社会中每个人最终都会面对的一个难题: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总能轻松满足我们的任何欲望,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个过于“友好”的社会?在这里,我指的不仅仅是智能电话、搜索引擎、奈飞、亚马逊等各种产品或服务商对使用者偏好的预测。事实上,整个消费者经济的大厦早已悄悄改变了自身的结构,并且日益围绕我们的个人兴趣、个人形象和内在幻想而运作。现在,在北美和英国,甚至在欧洲和日本,要过上一种完全私人定制的生活成了一种很正常的需求。我们用药物和音乐来调适我们的情绪;我们让食物适应我们的过敏症和生活观念;我们通过健身、油墨、金属、手术以及可穿戴技术来私人定制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车型来表达我们的品位和态度;我们可以搬去最符合我们社会价值观的社区居住;我们可以找到与我们的政治观点最一致的新闻媒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社交网络,使我们说的每句话、发的每条状态都得到赞美。伴随着每一次交易和升级,伴随着每一次点击和选择,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近,世界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我想,即使我们没有变成网游成瘾者,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改变世界的面貌,而这种趋势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显然,当我们从一个层次的满足迈向另一个层次的满足时,这种追求给我们带来了高额的成本。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最近一次房地产和信贷危机几乎葬送了整个世界经济。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过度放纵问题。即使经济正在缓慢地复苏,我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觉得不够充实和稳定:如今我们对自我表达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导致这种渴求似乎已经摧毁了日常生活的核心结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从个人感情到政治、商业,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塑造了新的常规和新的预期,从而使人类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以文明的、社会的方式行事了。我们无法做出长期的承诺。对所有不能直接或立即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和观点,我们越来越难以产生兴趣,我们甚至无法容忍这样的人和观点。我们的同理心弱化了,我们越来越难以相信人类之间有任何共同点,而一旦这种信念崩溃,民主制度也将随之面临挑战。
这种情况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40年前,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弗·拉希以及汤姆·沃尔夫等社会批评家就曾警告我们:我们日益增长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正在摧毁战后时代的理想主义与信念。在1978年的一次题为“自恋文化”的辩论中,克里斯托弗·拉希曾说:“个人主义的逻辑已经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社会斗争,我们在进行霍布斯所说的‘与所有人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摧毁了我们的快乐与存在的意义。”事到如今,当我们再回顾这些悲观者的言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还远远不够悲观。那个时代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在几十年后,以自我为中心和高度自恋会变成主流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恐怕他们也从来不曾猜到,如今,个人的自私想法会变成这个社会的共同想法。政府、媒体、学术界,尤其是商界,曾经帮助我们平衡对即时自我满足的不当追求,如今它们自身却越来越多地沉醉在这种自私的追逐中。一个又一个板块在这种文化中沦陷,不管在大的尺度上,还是在小的尺度上,我们的社会都日益变成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社会,却对这种追逐的后果不加考虑。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于其中的“冲动的社会”。
我所描述的这种传统文化已经超越了消费者文化的范畴。随着我们对即时回报的不断追求,一整套社会经济体系因此而启动,并不断自动升温。关于共同行动和个人承诺的传统观念在不断消退。我们的经济曾经创造过长期的、基础广泛的繁荣与富裕,现在却渐渐缺乏缔造这种繁荣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目前看来美国的经济似乎被锁定在一个过热—崩溃的循环周期中,而这种周期的幅度还在不断放大。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曾经能够合理地动用资源,鼓励人们做出实质性的创新并实现进步,如今却倾向于逃避复杂的长期问题(比如教育改革和气候变化,比如为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必须进行的金融改革)。让我们来正视这样的事实:3/4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本应成为社会重启的契机,本应使我们反思自动升级和关注短期收益的社会经济模型,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危机之后最关注的仍然是经济的能量、企业家的才华以及能在短期内产生最大回报率的创新。事实上,由于经济模型的失灵,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力负担对即时满足的追求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目前愤怒的民粹主义倾向导致很多国家面临政治瘫痪的局面。但即使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做出应有的改变和调整。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我们曾经理性而又团结的社会如今变得如此冲动并以自我为中心?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的我们?这些问题是本书将讨论的核心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经验。正像很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我在生活中常常需要与我们的经济体系艰难相处,因为该体系总是将我想要的东西和我需要的东西混为一谈。因此,我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习惯了资源稀缺的个人与物质极度丰富的经济体系之间强烈的不匹配现象。然而,我渐渐发现,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狡猾的市场与容易受骗的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而是个人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性的变化。比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战后时期,今天的这种高度自私的文化并没有如此露骨地占据主流。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今天自我中心主义的不断升温至少部分源于宗教和家庭等制度的弱化,因为这些制度曾经对自我沉迷的行为起到过限制作用。然而,这里还存在一种更为严格的经济层面上的叙事。美国战后时代无私精神的垮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时期,显然这种时间上的关联性不仅仅是巧合。经济危机削弱了我们的安全感,也增强了我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而经济上的成功也同样助长了自私文化的盛行,因为新经济理念和新科学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更快地、更高效地、更个性化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欲望。获得个人满足变得如此容易,因此我们常常难以确认自我和市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之所以面临困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在经济危机后的正常紧缩阶段,更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型的“侵略战争”。市场这台巨大的“侵略机器”一直在加速扫清它与消费者之间的一切障碍,而这场侵略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剧烈的最终阶段——市场与我们的自我、经济形势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
如果回到一个世纪以前,回到消费者经济产生以前的时代,我们一定会被技术的匮乏所震惊。那时候经济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感情生活是分离的。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很少参与经济活动,那个时代与现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发生的地方。一个世纪以前,大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我们的“外围生活”中,所谓“外围生活”指的是物质的“生产”世界。我们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农耕,我们制造手工艺品,我们修鞋,我们钉钉子,我们烘烤食物,我们腌制食物,我们酿酒……我们生产各种各样有形的商品和服务,其价值是相对客观和可量化的——它们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市场,还取决于我们物质的、外在的生活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很容易度量的。如今,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变大了许多,但是大部分经济活动(在美国约占70%)是以消费为中心的。我们消费的很大一部分都具有可选择性——这些消费不是由我们的“需要”驱动的,而是被我们内在世界的无形标准所驱动的:包括我们的理想和希望,包括我们的自我认知和我们秘密的渴望,包括我们的焦虑和我们想克服无聊的心情。由于我们的内在世界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由于公司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人们瞬间的喜好(这种瞬间的喜好会永不停息地产生),整个市场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于是,整个经济便逐步向人们的自我靠近。有些人甚至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革命以来,消费者市场已经进入了自我的内部。如今,市场不仅与我们的欲望和决策不可分割,甚至还与我们的自我认知不可分割。
通常来说,这种市场与自我的融合被描述成一种带有敌意的接管——如果没有商家几十年来的市场宣传和广告洗脑,也许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者经济的田园牧歌之中。但是,市场与自我的融合其实一直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一旦消费者成为经济活动和公司利润的中心,自我的死亡就已经注定。市场注定会冷酷无情地改变其复杂的结构和过程,来吞噬消费者的自我,因为只有消费者无穷无尽的自我欲望才能消化发达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产出,而这些产出永远不会停止增长。虽然被市场吞没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自我却会欢迎市场的吞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不断翻新的产出,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无法接触这么多美丽的幻想,无法将自我表达的力量持续不断地转移和放大。从这一角度来说,市场对自我的侵占实际上是市场和自我的双赢。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辩论这种融合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谈论这种融合现象的道德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可以讨论是否存在自我与市场的另一种关系,以及自我与市场的另一种关系是否会比目前的关系更好。然而这种融合现象本身已成定局。今天,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已经如此完善,这个系统受到如此强烈的认同,以至任何进步的意义都要靠这个系统本身来定义。这个系统塑造了我们的期望,控制了我们对成功与失败的度量。这个系统引导了对资源和才华的分配,尤其是决定了我们如何使用创新的巨大能力:苹果的成功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缩影——这个目前市值最高、品牌认同率最高的公司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而上述所有潮流都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事实上,如果不对目前的趋势进行严肃的修正,那么这种融合的现象将会随着新技术的产生而不断加速,因为新的技术会帮助市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最秘密的喜好,并且能够持续不断地调整和适应这些喜好的变化。市场和自我正融为一体。
但是,市场和自我的融合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如果我们把一个人从19世纪90年代或者20世纪70年代带到现在,恐怕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目前以取悦消费者为唯一目标的社会经济体系存在什么巨大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专家会告诉我们,一个被我们的冲动塑造的社会正是自由的象征;而一种由我们的欲望塑造的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因为这样的经济能够充分满足我们的愿望。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所说的那样,如果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他们的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甚至包括他们最微小的欲望),那么这些行为的总和就会让经济以最高的效率运转,并且向大多数人提供最高的效用。(用亚当·斯密的名言来说,通过追求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我们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领导,共同达到一个与我们本意无关的最佳状态”。)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好处,这一点不容否认。这样的经济产生了很多财富,很多创新,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很多个人的力量。你我都可以运用这种个人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为了获得这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创造的力量,难道我们不能忍受周期性萧条、党派政治以及过度自恋的文化吗?
也许,我们确实不能。虽然目前的经济希望向我们提供所有我们想要的,但结果是这样的经济并不能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越是有效地满足了个人的即时欲望,就越难达到一些长期的、对社会有利的条件。是的,这样的经济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却不再是以前那种稳健的、广泛分配的、让所有社会阶级共同受益的财富了。是的,我们的经济产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个人商品(从智能手机到金融创新产品,再到神奇的保健药品),却不再能产出足够多的公共产品(比如公路桥梁、教育和科技、预防性的医药产品和清洁能源)。这些公共产品对经济的长期稳定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公共产品的缺乏已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能制造出等离子电视机、座位加热器、牙齿美白产品以及能一步一步指引你到达最近的潮流酒吧的手机导航软件。但当我们需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金融体制改革、医疗体制弊病或者现实世界中的其他重大问题时,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我们常常用“政治失灵”来解释上述难题。这些问题确实反映了一种失灵现象,然而这种失灵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与消费者心理的过度融合。市场利用了消费者心理中最不应该被鼓励的部分,这种心理特点是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过度追求即时的奖励而忽略了未来的成本。我们的整个消费者文化把即时满足上升为人生最主要的目标,这种文化鼓励人们用最直接的、最有效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追求这个目标。这种追求即时满足的、忽略长期成本的倾向在整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个体和机构身上都有所体现,这些参与者和机构似乎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整个经济。追求利润永远是最优先的目标。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过去我们曾有过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和预期,认为利润和这些社会责任是不可分割的。如今,这些社会元素已经被贴上了“低效率”的标签,我们试图用最新的科技(比如自动化)和最聪明的商业策略(比如离岸金融)来减少或消除这些社会元素。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解释了为什么如今的公司利润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从公司利润的角度看,我们似乎早已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然而,也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导致我们的劳动者、我们的社区和其他的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而这些群体曾经天真地把商业世界当作一种能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
确实,商业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大部分物质进步的来源。因此,当我们批评现在的商业组织不应该一味地用技术来提高利润,而完全不考虑这些商业行为的社会效应时,我们并不是在表达反商业主义或反技术主义的呼声。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合理分配曾经提高过我们的整体社会效能,并且推动了很多社会目标的实现。如今,这些技术和资源却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金融工程”之类的领域,而我们都知道这些领域正给我们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利润曾经来自制造业,如今金融业却成了最大的利润来源。对于令人兴奋的大数据技术,我们不是用它来解决这个时代的很多复杂的问题(先不谈我们误用大数据技术的可能性),而是利用这项技术帮助市场进一步吞噬消费者的自我——我们用大数据技术开发出更多逼真的游戏,更多量身定制的个人技术,甚至把整个数据经济放在离大脑只有几厘米的数字眼镜上。
显然,这并不是经济运行的最优方式。但是,对于一个靠我们的幻想和恐惧来支配的经济体系而言,我们还能期望一些别的什么呢?从更本质的层面上说,对于一种把合作价值、耐心、自我牺牲看得一文不值的文化来说,我们还能期待一些别的什么呢?在目前的文化中,我们不再把自我陶醉和以自我为中心看作一种问题,反而把它们看作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样的文化中,自我已经变成了一种“产品类别”,我们欢庆着这种产品类别的合法化。这就是目前社会中我们的“自我”的真实样子,我们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那种强有力的、确定的、自信的自我,不再是沃尔特·惠特曼歌颂的那种自我,而是变成了一种腐败的、缺乏安全感的、高度妥协的自我。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冲动的社会中,所有对快乐和满足的强调,最终的产物却是焦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明白,以短期自我利益为目标的文化意味着灾难迟早要发生;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很多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每年都制造出更多的贫富不均现象,我们看到政治体系是如此的短视,可以被利益收买而做任何事情,这些现象都导致了愤怒情绪的日益堆积。在情绪的层面,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虽然冲动的社会强调个人兴趣的满足,强调“我”高于“我们”的哲学,但这一切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难以被满足。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的自由是一种神奇的特权,然而我们越是拼命地追求自我的满足,就越会发现一个古老的事实从未改变过:只为自己而活、只为当下而活的理念会严重埋没人们的潜能。
但是,好在我们仍有自救的潜能。上文提到的网游成瘾者布雷特·沃克就通过戒除网瘾拯救了自己。通过逃离网络游戏给予他的持续不断的即时满足,沃克发现在脱离这种自我沉迷之后,自己其实会变得更快乐。也许我们都应该学习沃克的经验。我们的社会通过制造对狭隘的即时满足的预期,把我们变成了和沃克一样的“瘾君子”,使我们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导致我们至今未能康复。通过康复治疗,沃克已经戒除了网瘾,而我们却尚未从即时满足的陷阱中逃脱。相反,我们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是重建危机前的经济——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正是这样的经济导致了本次危机的发生,重建这样的经济只会重蹈覆辙。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如果我们确实有意重振整个社会低落的精神面貌,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即时满足的社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情绪和金融两个方面。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质疑“效率”的重要性,通过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达到进展更快、成本更低的效果,这是完全合理的。效率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的效率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危机:贫富差距的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冲动的社会无法有效解决的各种根本问题所带来的危机。我想要批评的是盲目追求效率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弥漫于当代的政治领域,更弥漫于当代的商业领域,它让人们相信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高的产出永远是社会的最优先目标。我不否认这种意识形态曾经为我们带来过经济繁荣,但是现在这种意识形态却正在摧毁已有的繁荣。如果我们一心逃避所有劳动的必要,我们如何能修复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如果我们制造的所有产品(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所有成就、所有经验以及所有感情状态)在被制造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过时,我们怎么可能制造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不断升级换代的经济模型中,我们怎么可能保有传统,怎么可能理解永恒,怎么可能对未来做出长期的个人承诺呢?
我们的自我正变得越来越脆弱,通过这些讨论,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背后的原因。我认为这也正是我们的经济多年来持续低迷的真正原因。我们的经济之所以面临危机,并不仅仅是因为资产泡沫的破裂和非理性的经济过热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过于关注短期目标,对长期投资的观念极不友好;我们的文化忽略了长期承诺和某些真正永恒的东西,以致我们无法生产出任何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东西。在一个富有野心的“新兴”社会(如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时代,这些新兴社会仍以我们过去的价值观来定义产生价值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度关注短期和暂时价值的冲动可能会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致命弱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中,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非常“过时”的,甚至设想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意识形态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至少拥有选择的权力,去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平等的、审慎的社会吗?对于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所采取的那种政府严重干预经济市场的制度,我们也许应该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至少这些国家在努力让它们的经济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任由盲目追求效率的意识形态推动经济发展。从更本质的层面来说,这些国家用清晰的社会语言定义了经济发展和财富的标准。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这些国家的标准,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的“第一世界”用来度量进步的标准现在已变得不可持续了。我们急需一套新的体系来度量经济发展和财富的价值,仅仅用“每股收益”作为度量指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要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将我们带向何方?我们希望产出何种形式的财富?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财富,让财富的价值评估体系包含社会的可持续性目标,并平衡短期与长期的目标?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出一套系统,使得经济活动更多地考虑社会效应?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大众放弃即时满足和狭隘的自我利益,重新建立长期责任感,并建立一种永久性的、稳定的自我意识?
必须承认,在目前的政治文化中,要制定一套体系来平衡上述所有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看我们在医疗改革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方面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就知道了。我认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不仅反映出这些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反映出左派和右派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差异:对于市场的功能、政府的角色、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左派和右派都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在美国的政治领域,中间立场是不存在的。
但是,左派和右派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理念分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发明。当我开始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时,我还是一名无可辩驳的自由派人士,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框架非常不信任,并认为对快速的、高效回报的追求正在把我们的整个经济与文化体系碾为齑粉。然而,虽然目前我的经济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深入研究过这个冲动的社会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成因以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于得出保守主义的结论。我认为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最关键的社会因素正是那些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对家庭和社区观念的强调以及对自律等个人美德的推崇等。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兼顾双重目标:通过监管和提供激励机制建设一种更好的经济体系,它应对各种社会效应更加敏感;同时我们应该启发和说服民众放弃追求即时满足和狭隘的自我利益,重新建立长期责任感,并建立一种永久性的、稳定的自我意识。
我得出的这一结论并不独特,在过去40年中,很多社会评论家都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使我相信,目前的分歧(右翼和左翼的分歧、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分歧、全能政府和自由个人的分歧)显示的不是本质层面的不同的理念,而是错误的选择。政治上的党派分歧本身就是冲动的社会的产物:各党派放弃了对长期政治目标的承诺,转而选择收益率最高的党派主义策略。对长期政治目标的承诺曾经是工业化社会的政治特点,然而我们的经济模型和技术进步却使我们相信这样的行为是低效率的,从而使我们放弃了上述有益的态度。但是,这种目光更长远的传统政治态度并没有灭绝:虽然在冲动的社会的影响下,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极端主义盛行的现象,但我相信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仍然是比较中立的,而且做好了随时改变的准备。
在此,我认为与历史的比较是我乐观态度的真正来源。在历史上,美国曾经解决过很多大规模的、复杂的问题(比如世界战争、经济萧条、种族不平等),我们完全有能力再打一场胜仗。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确实更加艰巨。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维持现状是没有前途的。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在北西雅图地区的一家苹果专卖店中,我正与五六个中年客户一起参加新iPhone(苹果手机)功能的学习讨论班。曾经,星期五的傍晚是酒吧时间,属于半价酒精饮料和调情,但是如今购买个人技术用品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娱乐项目。本次学习讨论班的教练名叫奇普,是一个20多岁的瘦弱小伙子,由于店里的人太多,他必须使用扩音器才能让大家听清他的话。奇普戴着时髦的眼镜,脸上的表情安静又绝望,仿佛在老年旅游巴士上工作的年轻导游一般了无生气。现在,奇普正在教我们使用苹果公司最新的iPhone辅助技术Siri(苹果产品的一项智能语音控制功能),根据苹果公司的宣传,Siri无所不能,从文字输入到寻找可入住的酒店,再到搜索最好的美式烤肉店,没有什么事是Siri不能帮你做到的。Siri通过所谓的“调整型智能”为我们提供这种前沿的服务。 [1] 根据奇普的解释,所谓调整型智能就是,你对Siri说的话越多,Siri的反应和理解能力就会越强,Siri能帮你做的事情也就越多。苹果公司将Siri定义为一款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力App(应用程序),也就是说这种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更多的任务,因此被视作人机关系方面的一项重要进步。但是,奇普同时也警告我们说,这种强大的能力有时也会令我们感到不安。“老实讲,对着一个机器说话,让机器回答你,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这确实有些奇怪。”当奇普这么说的时候,他脸上带着一种排练好的同情的神色,仿佛试图让我们相信他自己也曾在与Siri对话的时候感到过尴尬和羞涩。奇普建议我们首先在家中进行充分的练习,然后再开始在公共场合使用Siri。“但是相信我,经过几天的练习,你们就能够泰然自若地公开使用Siri了。”
虽然奇普对Siri的功能进行了庄严的演讲,但是当Siri在2011年首次推出的时候,却受到了一些并不友好的批评。除了一些十分具体的抱怨(比如Siri听不懂布朗克斯口音)以外,还有很多评论对Siri“生产力促进者”的角色表示嘲笑。确实,在苹果的Siri广告中,Siri的使用方法(“Siri,给我来杯拿铁咖啡”,“Siri,快播放我跑步用的音乐”)看起来并不能提高生产力,而只是为无聊的雅皮士们提供一些随手可得的数字娱乐而已。 [2] 苹果一向善于制造一些技术乌托邦式的媚俗洗脑广告(苹果平板电脑被形容为“一扇魔力的窗口,让你与你所爱的东西之间保持零距离”),来辅助公司以激进闻名的新产品推出战略(一旦该产品的利润空间下降,苹果公司就立刻推出新的产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Siri只是苹果向客户提供的一根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胡萝卜而已。
几天之后,我让Siri帮我设置一个5分钟的计时器,而Siri立即照做,虽然我对苹果公司的产品抱有不太友好的想法,但在那一刻我仍然感到惊喜与激动。我让Siri通知我的儿子,因为越野训练我必须迟一点去接他,Siri立刻给我儿子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中的文字与我的口述一字不差。我要Siri帮我查找昨晚西雅图水手队的比赛分数,我让Siri告诉我明天的天气,我让Siri大声读出我收到的短信,这些任务她都一一照做,分毫不差。虽然一开始有些尴尬,但随着Siri渐渐熟悉我说话的规律,她对任务的完成也变得越来越顺畅。我无法否认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的快乐,当我开始下载其他生产力型的App(包括网上银行集成App,记录我慢跑时卡路里消耗的App,让我俯瞰这个城市甚至可以偷窥邻居后院的App)时,我的内心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激动与快感。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工具号称可以提高生产力,实际上我非常确定因为玩手机我的工作效率下降了,但是,这些App确实让我感觉很棒,这种激动和快感是深层次的、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当我们的祖先能够轻松快速地找到食物、住宿、性伴侣的时候,他们脑中也曾释放过同样的化学物质。我意识到,苹果公司真正的产品是这种生物化学性的刺激。很多人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徒有其表而实质空虚。但实际上,苹果公司和其他个人技术公司(比如谷歌、微软、脸书等)所售卖的产品确实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就是让人们通过最少的努力,快速获得最高水平的瞬时快感的能力。
显然,这并不是亚当·斯密式的生产力。对经济学家而言,生产力意味着效用的最大化、成本的削减和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比如用更有效率的方法产出一桶谷物,使得单位粮食产出所消耗的劳动力时间更短)。那种经典意义下的生产力帮助我们的祖先免于饥饿和贫穷,免于物质的匮乏。但是,要评判苹果公司的压倒性成功(目前苹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孚石油公司,虽然后者的产品对人类来说更加必不可少),以及个人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消费者每年在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上花费250亿美元),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新的、更个人化的生产力,从某种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与其他的生产力一样重要。我们不仅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为这些技术埋单,而且我们像原始社会的猎手和采集者一样,高度关注这方面的动向,期盼着这种生产力的每一点新进步。只要新的产品上架,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第一时间将它们买回来,这种狂热和我们的祖先对新武器和新工具的狂热如出一辙。这种随时随地对更高效率和更高生产力的狂热追求,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也是本书的出发点。
靠我们对生产力的狂热追求来赚钱的公司早已有之,今天的大型技术公司根本谈不上是这方面的先驱。早在100多年前,欧洲和美国尚处于混乱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人们周期性地面临着经济的崩溃和物资的短缺,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完整的行业,来帮助我们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产出。人类社会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专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教会经理人如何让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效率优化者》一书的作者爱德华·普林顿,告诉读者如何把低效率的活动从生活中清除出去,这些低效率的活动包括午后茶会、有礼貌的谈话、使用4套餐叉的餐桌礼仪。 [3] 但是更强大的生产力专家,是工业主义的实业家们,他们建起了超高效率的工厂,大规模生产世界上的第一批生产力产品:灯油、罐头汤、连发步枪、打字机、洗衣机以及其他让我们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的工具。在这些实业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亨利·福特,在他的努力下,大规模的汽车生产成为可能,这一创新对个人产出起到了前所未见的促进效果,甚至完全改变了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个人的定义。
亨利·福特是为提高个人生产力而生的。他出生在底特律郊外的一个农场,对于农民来说,只要任何新的工具和方法能让他们用一小时的人工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这些工具和方法就能充分激发他们的狂热和激情。对生产力的这种农民式的追求流淌在亨利·福特的血液中,他将这种追求作为他所开办公司的核心原则。当他的竞争对手还在为镀金时代 [4] 的子孙们手工制作豪华轿车的时候,亨利·福特已经创造出了福特T型车,他的目标是以足够低的成本为大多数人生产汽车。为了做到这一点,亨利·福特不仅生产出了简单耐用的汽车,还创造了一个新的生产系统,这个新系统的核心是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这个高效率的系统使得亨利·福特能够大批量生产汽车,从而取得规模化效应带来的效率提高。随着福特汽车公司每月的汽车产量越来越高,每辆汽车所分摊的固定成本越来越低。换句话说,生产一辆汽车变得更便宜了,这使得亨利·福特能够逐渐降低汽车的单位售价,从而吸引更多的购买者;而销售量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汽车的产量,导致汽车售价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1923年,亨利·福特已经把福特T型车的售价从每辆85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1 000美元),降到了每辆29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4 000美元)。这个价格相当于一位普通工人年工资的1/3,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只相当于马车价格的一半,而马车是当时标准的个人交通工具。
换句话说,中等收入的市民也买得起汽车,也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力升级。当时的马车每小时约能行进8英里 [5] (需要随时暂停让马匹休息、进食、饮水),而福特T型车可以轻松达到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并且可以连续行驶200英里不用加油,这就让个人的交通能力提高了5倍。当然,在拥挤的都市中,汽车可能无法充分发挥速度上的优势。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住在美国的农村地区,这里遥远的距离造成了经济和社会上的深度隔离,因此汽车所带来的个人权力的提升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一个农民家庭往返最近的城镇只需一小时,而以前这需要花费整整一天。现在,医生可以及时赶到农村居民的家中挽救患者的生命。销售员可以在5倍于从前的地域范围内推销。年轻的夫妇们(我们的曾祖父母)可以逃离压抑、刻板、受左邻右舍监视的乡村生活。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随着福特的技术突破,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汽车就变得如此便宜和普及,“小镇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轻松驱车20多英里去路边的旅馆跳舞,而无须忍受邻居监视的目光”。 [6] 从前只有精英阶层才能享受的自由,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而正是随着这种自由的普及,产生了“自我”这一概念。
福特的新生产技术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个人汽车的领域。20世纪20年代,福特发明的新商业模型几乎重塑了美国的整个经济模式。随着其他生产厂家学习福特的方法,市场上出现了无数种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新工具,从家用电器到半成品食品,再到电话和收音机,每一种产品的上市都标志着个人权力的进一步提升。虽然并不是每种商品的影响力都和汽车一样大,但是在那个普通人必须依靠某种巨大的非个人力量施舍的仁慈才能生活下来(尤其是商业精英可以为了追求个人利润,而随时无情地碾压普通人)的时代,个人权力的小小提升就能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为了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需求,新的企业家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更多的工厂被建立起来,人们发明了更高效的生产线和生产工序,这些新的工厂发放给工人的工资又催生出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进一步催生出更多的工厂、更高的工资、更多赋予个人权力的商品。
随着整个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经济参与者的自我的认知也在快速改变。美国曾经是一个生产者的国度,我们每天重复着缓慢的农耕和手工制造的工序,我们在有限产出的范围内生活。如今,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者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劳动挣得工资,然后用工资直接购买需要的成品,这些成品通常比家庭制造的产品更便宜,质量也更好。一个世纪以后,哀悼过去的生产者经济成了一种时髦。现在,在我们的想象中,过去的生产者经济是那样真实、简单和纯粹。然而在生产者经济消亡时,却很少有人表现出悲哀和惋惜。像亨利·福特这样的新消费者经济创造者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知道那个时代其实充满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的物资短缺,以及镀金时代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对他们来说,新的消费者经济不仅意味着生活标准的大幅提高,而且是确保这种进步不断持续的动力。消费者经济仿佛一台神奇的永动机,每年都让普通的个人获得更多的权力。
然而,这场个人权力的革命只成功了一半。人们发现,亨利·福特发明的这种循环战略(通过降低价格提高销量,然后再通过销量的增加进一步压低价格)事实上有点像一台不准人们停步的跑步机。商家要想保持利润,就必须不断售出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力。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到达某一点之后,消费者就无法再消费更多的产品了。虽然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大部分劳动者仍保持着一种19世纪的俭朴生活态度,他们买回一件工具,就会一直使用,直到它坏掉(在工具坏掉以后,他们还会试图修好它并继续使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家庭都已经拥有了一辆汽车,然而由于亨利·福特生产的汽车非常耐用,很少有家庭需要再次购入汽车。 [7] 于是汽车的销量增速减缓了,亨利·福特的利润也降低了,福特汽车公司不得不开始削减产量,这导致了规模效率加成的损失,并且威胁到了整个商业模型的成功。面临这个难题的不仅是亨利·福特一个人,大部分生产厂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为了达到福特式的规模和市场份额,这些厂家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工厂、生产线、分销网络以及产品展示商店。然而,只有巨大的销量才能帮助厂家收回这些成本,但这些过量的产品已经超过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于是福特和其他实业家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大幅削减产量,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血本无归,要么设法劝说人们购买和使用更多的个人权力。
最终,商家选择了后一条路:说服消费者购买更多的产品。这方面的先驱是另一位汽车生产者——福特在商业和哲学上的最大竞争对手,通用汽车的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福特是农民的儿子,他不喜欢过多华丽的展示和包装,而斯隆则生于富裕家庭,受过最好的教育,习惯了高品质的生活。在汽车制造方面,福特采取的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关注的是每个零件的功能,是汽车的技术性能。而斯隆认识到,大规模生产消费者商品的关键已不再是技术,而是心理学:如何劝说消费者,让他们更开心地掏出口袋中的工资。
斯隆的心理学战略包括两个阶段。首先,通用汽车公司推出了一项崭新的服务:通过内部银行提供便宜的消费者信贷。当时,大家对消费者信贷的接受度还很低,大部分人觉得向金融机构借钱与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区别。福特认为,借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销售汽车时只接受现金付款。斯隆的举动大胆而充满智慧。提供消费者信贷服务不仅让斯隆的客户有能力更快地买车(而不需要经过储蓄的过程),还让他的消费者有欲望购买更多的汽车,而卖出更多的汽车正是斯隆的目标。传统的制造商只向消费者提供很少的选择,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只生产一种基础的车型,并且只提供一种颜色——黑绿色。而通用汽车公司却为顾客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从经济实用的雪佛兰到顶级豪华的凯迪拉克。通用汽车的全线产品经过精心的设计,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购买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汽车品牌,然后还可以通过升级到更好的车型来体会地位提升为自己带来的巨大快乐。事实上,通用汽车不仅向顾客提供了交通工具,还为顾客提供了一种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渠道,当时的美国人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在意,因此斯隆的这种发明实在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其次,最重要的是,斯隆向消费者提供了一条可以永不停歇地提高自身地位的魔力通道。1926年,通用汽车引入了“年度模型升级”的商业策略,公司每年都对所有车型进行改进。其中有些改进确实是可度量的、实质上的改善,比如更好的刹车系统或更安全的传动系统;而更多只是表面的装饰性改进,这些改进的目标是给消费者提供一种感情上的激励,比如拥有整个街区最新潮的车辆带来的快感,比如暂时逃离家庭与工作的冗繁任务,开车去兜风的快乐。(斯隆的首席汽车设计师亨利·厄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我希望我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汽车,每次你坐进去都感到由衷的快乐和放松,开我们的车就像享受一次短暂的度假一样。” [8] )事实上,斯隆并不是第一个利用消费者的软性偏好的商人。几百年来,富裕阶层一直通过金钱来购买地位感和其他令人愉快的感情体验,索尔斯坦·凡勃伦把这种消费行为称为“炫耀性消费”。通过大规模生产、每年的设计更新以及宽松的消费者信贷,斯隆也向普通消费者提供了同样的自我满足途径。在新的消费者经济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断购买升级换代的产品,来追求更高层次的情感满足。在过去的生产者经济中,消费者只有经过长期的自律和努力才能获得一瞬间的强烈满足,然而在新的消费者经济中,人们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获得这样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斯隆创造了一种新的个人生产力,这是一种情绪性和启发性的生产力,人们通过很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难怪我们会像农民追求更高效的拖拉机一样,迫不及待地拥抱这种新的现象。
这种冲动和欲望并不是由斯隆发明和生产出来的,我们喜新厌旧的原因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新的东西代表着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可能交上好运。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内在渴望,因为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个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与集体的权力关系,因此社会地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我相信,斯隆并不太了解原始人的神经化学,但是他一定非常清楚人类天生具有追求新事物、追求社会地位的本能。更重要的是,斯隆知道这种对欲望的满足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我们离开汽车展示商店,新事物带给我们的快感就开始消退。随着新车型的推出,去年的旧车型带给我们的地位感马上化为乌有。保持快乐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更新自己拥有的产品,而这正是制造商最需要的。现在,不仅生产者走上了这台让人永不停歇的跑步机,消费者也爬上了这台机器。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广告,只要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刺激,消费者的这台跑步机就可以完全适应生产者跑步机的需求。斯隆把这种商业策略称为“动态淘汰”,而且他并不避讳谈论这种策略的目的。斯隆曾说:“每年我们都尽可能造出最好的汽车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下一年我们会继续造出更好的车型,让消费者再次觉得不满足。” [9] 至此,斯隆找到了解决现代工业机器过度生产问题的完美方案。从此,无论商家生产出多少过剩的商品,消费者无穷无尽的欲望都可以将其消化掉。
很快,大家都发现了斯隆这种销售策略的天才之处。通用汽车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而动态淘汰策略则成为新经济的典范。这种动态淘汰策略把消费者的心理和工业产出的偏好联系起来,把自我和市场联系起来。曾经由工程师和会计师控制的大型制造公司开始雇用大批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师,一位业内人士曾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关键是消费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动态地决定了人们想要购买什么,不想购买什么。” [10] 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战争。在商家的努力下,消费者开始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购买商品:我们不仅为追求新奇感和社会地位而购物,我们还为重振受损的自尊而购物,为缓解平庸的婚姻带给我们的失望而购物,为逃脱办公室工作的烦琐和奴役而购物,为反抗城郊生活的甜腻感和令人窒息的统一性而购物,为摆脱疾病和衰老带给我们的无力感而购物。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是批评消费主义文化的先锋之一,林德指出,如今的产品通过市场化营销被消费者所购买和使用,这些产品的作用类似于药物治疗:通过购买和使用这些产品,消费者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类型的感情和社会问题。 [11] 林德和其他一些学者对这种治疗型的消费主义极度反感,然而并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呼声。伴随着每一次产品周期和模型升级,消费者产品赋予我们无穷的权力,现在我们不仅能够掌控外部世界,而且可以如上帝一般全面掌控我们的内在世界了。
至此,距离这个消费主义的个人权力时代只有一步之遥了。当我们的身份从生产者转为消费者,我们的身心已经完全被市场所掌控,我们不仅需要商家生产出来的产品,还需要从这些商家那里挣得工资来购买这些产品,这实在是一种不太安全的处境。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劳动力仅仅被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劳动者要看雇主的脸色生活。当时的雇主经常压低工资,甚至使用暴力(或者贿赂当权者)来阻挠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最富裕的一小部分人与大众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消费者发现市场所提供的产品有时并不是最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产品。很多新的产品和服务是有缺陷的、危险的,甚至是欺骗性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有些新产品的功能太好太强,为消费者提供了过大的个人权力,消费者根本无法安全、可持续地使用这样的权力。比如,当时的汽车速度已经超过了主要公路系统能够承受的安全范围(20世纪20年代,美国每天、每英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现在的17倍)。过于宽松的消费者信贷鼓励美国家庭大量借款,为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后续的大萧条埋下了伏笔。商家为消费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让消费者可以获得个人欲望的满足,却同时让社会承担相应的高昂成本。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十分盛行,而当时这些便利曾被视作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的特权。
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失衡现象。随着我们从生产者经济转向消费者经济,私人商品(比如汽车和消费者信贷)的产出越来越多,而公共产品(比如高速公路安全和稳定的信贷市场)的产出却严重不足。市场逐渐向个人的兴趣倾斜,而忽视了对社会利益的关注,这种倾斜是逐渐的,但从未出现过逆转的趋势。当然,这种倾斜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产私人商品(尤其是那些为个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人权力的商品)获得的利润要远远超过提供公共产品获得的利润。然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逻辑,从公共产品转向私人商品的这种倾斜都会导致现代社会的核心难题:如果不重新调整,社会的经济利益将缓慢但不可逆转地被个人利益所侵占。
当然,这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并不是永远无法扭转的,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改革者就已经设法通过大规模、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扭转市场(包括公司和个人)过度追求短期满足的不良倾向。标准石油公司和铁路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被打破,并受到了合理的监管。法律规定了资本家必须向工人支付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保护工人的联合谈判权(这种谈判权最终导致公司必须与工会握手言和)。通过建立法律和监管制度,消费者免于受到不安全的产品、有毒的食品以及居心不良的放贷者的伤害,过于短视的投机分子所造成的巨大风险也受到了限制。政府还通过在教育、科研,特别是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灌溉系统和土地开垦项目)方面的大量投资,扭转了公共产品投资不足的现象。政府投资的增加进而刺激了私营板块的投资增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即时满足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是可以被制服的。正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必须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忠诚军队那样前进,必须为了共同的原则而牺牲”,“必须随时准备为了维护这种共同的原则而放弃我们的生命和财产”。 [12] 换句话说,如果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不能或不愿意生产足够的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就要想办法迫使它增加公共产品的产出。
这种对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重新平衡被罗斯福称为“新政”。这种“新政”的成果是非常惊人的。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时,不仅经济产出已经完全从大萧条中恢复,而且已经完全准备好研发新一代的高科技消费品,并开创更高水平的经济繁荣,而这得益于政府和企业的投资。 [13] 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一波经济繁荣被推迟了,但短暂的推迟只是让美国的消费者经济积蓄了更强的潜力和能量。在接下来的4年中,政府为了提高工业产出进行了大量的政府支出,支出总额约合今天的43 000亿美元。 [14] 一方面,大量新的工厂、生产工序和技术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战争时期的配给限制制度节制了消费。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人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储蓄金额约合今天的15 000亿美元,这笔积蓄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 随着战后时期的开始,这笔巨大的资金及其代表的被长期压抑的欲望,立刻流向工业板块,此时美国的工业板块已经远比战前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更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战后美国的环境为大规模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消费者的需求高涨。通用汽车、福特、埃索、通用电气、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杜邦等美国公司不仅变得比战前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而且由于战争扫除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这些公司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没有任何对手。自然资源非常便宜,原油价格只有今天的1/4,而能够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又在飞速地发展。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率(劳动力每工作一小时的产出)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在接下来的25年中,美国经济的规模几乎达到了之前的三倍, [16] 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了以前的两倍。 [17] (日本和西欧的情况也与美国相似,在日本和西欧,靠美国纳税人支持的战后重建项目很快使它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以前的三倍。 [18] )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繁荣比以前任何时期的经济繁荣都具有更广泛的基础。实际上,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比顶层的人收入增速更快:不断向社会阶层的更高处迈进成为美国社会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已经上升了一半以上, [19] 也就是说美国有2/3的家庭已经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20]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是通过政府对市场的不断干预实现的。华盛顿当局非常希望避免战前经常发生的劳资双方暴力冲突(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常常在这种冲突中扮演暴力角色)。由于当时美国最大的国际政治竞争对手苏联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劳动者的天堂,因此美国政府面对政治上的压力,也希望抓紧推出对劳动者更为有利的政策。在这样的风潮下,工会和雇主进行了和解,白宫公开支持工人通过与雇主签订协议来获得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公司生产率提高的部分利润分成。在美国的战后时期,工会提供的劳动合同将工人的工资与工业生产率挂钩,而当时工业生产率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长。 [21] 此外,美国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征收70%~80%的边际税率,这一政策也使得公司不愿意像镀金时代那样向高管支付高额的工资[20世纪70年代,美国CEO(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只有员工中位数收入的20倍左右,远远小于今天的比例。]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私营板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很多公司已经不情愿地接受了更重视社会福利的经济形势。许多公司与工会达成协议,雇主开始对其雇员进行长期投资(比如,向雇员提供各种培训,保证雇员能够适应高速变化的技术发展)。职工获得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的现象日趋普遍。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像一种私营的福利组织。也许彼得·德鲁克这样的管理大师所提出的公司社会责任论并没有真正打动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们,但是作为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生产者,公司日益意识到它们自身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当通用汽车的前CEO查尔斯·威尔逊被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名为国防部部长的时候,他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中被问及是否会做出对他的前雇主不利的政策决策。面对这个问题,威尔逊回答说,他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决策,但他同时表示做出这种决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国家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威尔逊表示:“对我们的国家有利的政策也会对通用汽车有利,对通用汽车有利的政策也会对我们的国家有利。在这方面,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因为通用汽车公司的规模太大了,公司的利益影响着国家的福利。”
当时,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的完美平衡,高速增长的个人能力被强有力的社会结构所平衡。个人享受到了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带来的财富与福利,却不再受战前经济不安全因素的困扰,这是那个黄金时代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至少是美国白人男性的平均收入)已经是他们祖辈的两倍以上。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了1/3,却可以享受雇主提供的各种福利、终身就业保障以及退休金。 [22] 美国人的住房条件也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人们的平均住房面积几乎达到其祖辈的两倍(而家庭的规模大约减小了一半)。很多人住在郊区的别墅中,远离城市的喧嚣,房屋配备先进的空调设备和各种节约劳动力的家用电器,同时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就有高质量的学校和各种娱乐场所。美国的医疗条件和公共健康条件当时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美国人获得了更好的营养,因此平均寿命比祖辈延长了6年。 [23] 寿命的延长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使美国人有更多休闲的时间来娱乐和自我提高——阅读、旅行、欣赏艺术、参加夜校课程,这一系列活动使得美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对自我的满意度也日趋提高。美国精神病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主席、精神病专家保罗·豪恩在1946年接受《生活》杂志采访时说:“不管个人的潜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个人的各种潜力。” [24]
发展个人潜力的过程自然伴随着大量的消费行为。消费日益成为情感成长和自我发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随着商家每年推出新型号,每季推出新产品,我们在消费中不断寻找着真正的自我。无论转向何方,各种各样的消费选择都在邀请我们通过花钱来寻找真正的自我。战后时代的著名消费者市场推广专家皮埃尔·马蒂诺曾经说过:“几乎所有商业行为背后的动因都是消费者的个人理想,即消费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强调自我表达的时代,消费者选择某种产品、某种品牌、某种机构,往往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25] 甚至连工作、育儿、婚姻等传统社会功能也被巧妙地转化为各种自我表达的模式。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的研究显示,到了战后时代的晚期,很多中产阶层的美国人甚至认为爱情本身也是一种“互相探索无穷丰富、无穷复杂和令人无比兴奋的自我”的机会。 [26]
不难想象,这种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让我们疲惫不堪、压力巨大,甚至让我们觉得内疚。事实表明,虽然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期间,大部分人都获得了更大的个人权力,但是某些族群(比如妇女和有色人种)获得的权力提升幅度比其他人群要小。同时,也出现了对消费主义过度盛行的担忧,有些人担心我们追求真正自我的欲望会导致过度消费的正常化。《纽约邮报》的评论员威廉·香农曾经说道:“我们进入了一个猪的时代,如今在这片土地上最嘹亮的声音就是贪婪自私的猪叫声。” [27] 我们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我们花多少钱,不管我们如何精细地修饰自我,不管我们达到多高的水平,我们永远有更高的目标需要实现,永远有下一次升级在等着我们。这种永不停歇的追求让我们深感不安。
但是,不用着急,工业化的进步向每位公民提供了克服上述困难的工具。商家每年制作大量新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甲丙氨酯、氯氮等越来越多的药物帮助我们解决情绪上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个人技术发展的高潮来临了,一波又一波的新产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高保真音响及其他电子消费品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的空闲时光塑造得完全符合我们的个人品位。对战后的普通美国人来说(至少对中产阶层的白人来说),他们每年都能获得更多的个人权力,都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高的选择权。各种永不停歇的跑步机越转越快,个人权力提升的速度也越来越高。人们不再辛苦地工作以求“生存”,而是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个性化的“生活”之中。1964年,《生活》杂志曾刊出过这样的话:“现在,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这样的工具和知识,用以创造出任何我们想要的世界。”
那么,我们想要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看起来,那仍然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虽然有的人认为这片土地上充满了贪婪自私的猪叫声,虽然我们日益沉溺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中,但当时的普通美国人在必要时仍然“愿意为了共同的原则而牺牲”。当约翰·肯尼迪提出“美国人到底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的问题时,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为国家奉献是一件十分合理的事。情况并不像批评家说的那样严重,经济的繁荣和个人权力的增长似乎让美国人愿意更深入地参与广泛的社会活动。美国人参政议政的意愿变得更强了:20世纪60年代初,全民投票率比半个世纪前高了许多。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也提高了:志愿者和出席教堂活动的人数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国际狮子会和扶轮社等服务性组织,家长教师协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组织之一。1964年,一位评论人曾说,美国人“现在正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这些活动的目的包括改善当地道路、清理垃圾以及监督公务员履行职责等”。美国人也并不是只愿意做一些容易做到的好事,20世纪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冒着巨大的社会和个人风险参加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不平等现象的抗议游行活动。即使有些事情是个人无法做到的,我们也会积极促使政府代表我们完成这些任务。与今天的美国人相比,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支持政府为此而增加支出。 [28]
虽然美国人不断追求更高的个人权力和个人能力,虽然市场急不可耐地想要满足大家的上述愿望,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时的美国人仍然愿意为维护社会利益而牺牲部分个人权力,大家普遍认同社会关系是社区和个人生活的基石。20世纪美国公民生活的记录者艾伦·埃伦霍尔特指出,战后的美国是一个忠诚的国家。美国人“不仅对他们的婚姻伴侣忠诚,也对他们的政治选择忠诚,甚至对他们支持的棒球队忠诚。公司也长期保持对它们成长于其中的社区的忠诚”。虽然这种忠诚也许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但埃伦霍尔特写道:“这样的忠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个人的安全感,对那时的人们来说,社区是安全和熟悉的。当我们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从不担心明天会丢掉工作或者离婚。我们拥有充分可靠的规则,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或者等我们足够成熟的时候也可以反叛这些规则。我们相信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充分地执行这些规则。” [29]
这些现象对当时的社会学家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尤其是对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这样的“人文主义”学者来说,这些事情简直是理所当然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斯洛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论,这套理论的核心是需求的不同层次。这种理论把物质的富足和人们高层次的社会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马斯洛的理论核心非常简单:随着人们的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房以及物理安全保障)得到满足,他们的欲望自然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爱和社区地位。随着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人们最终会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马斯洛认为,这种完成了“自我实现”的个人不仅对社会非常有用,而且能体会到高度的快乐,他们还展现出马斯洛所称的“民主的性格结构”:这些人一方面独立并富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具有很高的道德节操和宽容能力。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自我实现的个人非常愿意参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简言之,这种自我实现的个人是完美的个人,每个人都希望身边有这样的邻居、老师或选民。
该理论的重点之一是,人们在追求这些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基本的物质满足:不管是低层次的基本需求,还是后续的更高级的、更复杂的需求,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没有物质和金钱,我们就无法攀登这座自我实现的阶梯。然而,随着物质条件的满足,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欲望会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和我们自然具有的所有其他本能一样强烈。马斯洛曾经这样写道:“只要一个人能够做到,他就必须做到。就像音乐家必须创作音乐,艺术家必须画画,诗人必须写诗一样,我们要获得终极的快乐,就必须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潜力。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促使我们去寻找最适合我们的角色。” [30]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是离这个目标越接近,民主的性格结构就会表现得越明显和深刻。对马斯洛来说,人类民主的实现不仅是一种政治的、集体的进程,同样也是一种心理的、个人的过程。马斯洛认为,每个个体自我实现的过程最终会导致一种集体性的转化:整个社会会向更高的需求层次移动,整个社会将变得更加智慧和民主。换句话说,“社会的层次和个人需求的层次是相对应的”。 [31]
马斯洛对大众自我实现的乐观看法仅仅是一种看法而已。20世纪60年代末,密歇根大学一位名为罗纳德·英格莱哈特的政治学者测量了富裕程度与更社会化的、更民主的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战后欧洲政治动向的过程中,英格莱哈特发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现实中确实得到了体现。二战爆发之前出生的人,由于成长于不安全的时代,更重视经济稳定、政治秩序以及其他传统的物质价值(他们愿意为取得这些价值而牺牲部分个人的自由)。二战后出生的一代却拥有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由于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婴儿潮”一代的人更愿意追求一些并不那么急迫的目标,比如娱乐和休闲,教育、文化、旅游、政治以及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婴儿潮一代的人由于成长环境更为优越,他们不仅会追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还愿意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越是习惯于这种自我表达的自由,就越愿意努力保护和扩展这种自由。他们保护和扩展这种自由的途径是支持自由的社会制度,比如民主、言论自由、性别平等、劳工权益以及环境保护。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通过翔实的调查数据,英格莱哈特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重视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于所有物质条件明显改善的国家和地区。 [32]
英格莱哈特的这种沉默革命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进步。这种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很多大规模的政治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是战后一代在从种族平等到越南战争的各个方面挑战父母一辈的权威。从环保意识的提高到对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宽容,再到长期被压抑的世界各国人民对民主的不懈追求,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英格莱哈特的沉默革命理论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后物质主义向我们展示了文明的前进方向。英格莱哈特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随着更重视物质的老一辈人的死亡,这个社会会逐渐接受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此外,英格莱哈特还预测,我们将在21世纪末迎来一个转折点,届时后物质主义将全面超过物质主义。一旦这种转折发生,我们将迎来全球性的后物质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整个社会都会全力帮助个人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
虽然英格莱哈特的沉默革命理论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这个理论也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最明显的是,如果社会进步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那么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甚至完全停滞,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情况呢?我们是否会退回更低的需求层次,从而变得更加物质主义呢?这种回归物质主义的倾向会不会导致与英格莱哈特所描述的方向相反的另一场沉默革命呢?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美国经济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也无法继续提高工作岗位的数量和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开始抬头,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公司的生产率增速下滑了,我们的工人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以更高的效率创造财富。更严重的是,随着美国的衰落,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却在重建中焕发出强大的活力,美国面临着新的国际竞争。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中东国家提高原油价格,美国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最需要的原材料变得更昂贵了。如果美国经济真的陷入困境,我们的社会进步是否也会全面停止呢?
如果情况和上述讨论的完全相反,我们又会怎样呢?假设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持续高速进步,为个人提供越来越多的表达自由,我们会不会因此觉得不再需要支持高层次的、后物质主义的共同原则了呢?事实上,英格莱哈特在后续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这样的规律:随着社会日益接受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中的个人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从而更不愿意支持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然而,英格莱哈特和他的同事认为,个人主义的盛行并不会导致狭隘的利己主义。他们认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对社区和社会富有责任感。 [33] 然而,很多例子却显示,当消费者疯狂追求急剧上升的个人权力时,他们会表现出一些愚蠢自私的行为,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汽车。随着汽车的普及和发展,车辆变得越来越大,动力越来越强,到20世纪60年代末,个人汽车不仅对整个国家的公路安全造成了威胁,甚至还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汽车的普及还导致美国过度依赖原油进口,并减少了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显然,汽车问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个人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越来越容易地在不经周围其他人同意(甚至是损害他人权益)的情况下追求个人的利益。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的后物质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何方呢?
也许,上述两个方向的发展是可以同时进行的。随着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段的结束,我们进入了更加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从而我们有机会观察美国社会是如何同时表现出上述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的。
[1] Andrew Nusca, “Say Command: How Speech Recognition Will Change the World,”SmartPlanet , Issue 7, at http://www.smartplanet.com/blog /smart-takes/say-command how-speech-recognition-will-change-the-world/19895?tag=content;siu-container.
[2] Apple video introducing Siri,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ciagGASro0.
[3] The Independent , 86–87 (1916),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 IZAeAQA AMAAJ&lpg=PA108&ots=L5W1-w9EDW&dq=Edward%20 Earle%20Purinton&pg=P A246#v=onepage&q=Edward%20Earle%20 Purinton&f=false.
[4] 镀金时代:指美国内战后的繁荣时期,约1870—1898年。——译者注
[5]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6]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perCollins,1976),p. 66.
[7] James H. Wolter, “Lessons from Automotive History,”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Marketing, Quinnipiac University,New York, 1983, p. 82.
[8] Quoted in David Gartman, “Tough Guys and Pretty Boys: The Cultural Antagonisms of Engineering and Aesthetics in Automotive History,” Automobile in American Life and Society, at http://www.autolife.umd.umich.edu/Design/Gartman/D_Casestudy/D_Casestudy5.htm.
[9] V. G. Vartan, “‘Trust Busters’ Aim Legal Cannon at GM,”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0, 1959, p. 12.
[10] G. H. Smith, 1954, in Ronald A. Fullerton, “The Birth of Consumer Behavior: Motivation Research in the 195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Bienni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Marketing, May 19–22, 2011.
[11]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n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with a Foreword by Herbert Hoov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pp. 866–67, at http://archive.org/stream/recentsocialtren02presrich#page/867/mode/1up.
[12] Franklin D. Roosevel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33, available at History Matters:The U.S. Survey Course on the Web,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5057/.
[13] Alexander J. Field, “The Origins of 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Golden Age,”Cleometrica 1, no. 1 (April 2007): 19, 20.
[14] Alexander J. Field,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U.S. Productivity Growth,”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 no. 3 (2008): 677.
[15] Gary Nash, “A Resilient People, 1945–2005,” in Voic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ume 1 (New York: Pearson, 2005), p. 865.
[16] “US Real GDP by Year,” http://www.multpl.com/us-gdp-inf lation-adjusted/table.
[17] “US Real GDP per Capita,” http://www.multpl.com/us-real-gdp-per-capita.
[18] G. Katona et al., Aspirations and AfAu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p. 18.
[19] For 1945 median income, se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2, Washington, DC, March 2, 1948, http://www2.census.gov/prod2/popscan/p60-002.pdf; for 1962 median income, se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49, Washington, DC, Aug. 10, 1966, http://www2.census.gov/prod2/popscan/p60-049.pdf.
[20] Nash, “A Resilient People, 1945–2005,” p. 864.
[21] Gregg Easterbrook,“Voting for Unemployment: Why Union Workers Sometimes Choose to Lose Their Jobs Rather Than Accept Cuts in Wages,” The Atlantic, May 1983, http:// 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83may/eastrbrk.htm; and Timothy Noah, “The United States of Inequality,” Salon, Sept. 12, 2010,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 and_politics/the_great_divergence/features/2010/the_united_states_of_inequality/the_ great_divergence_and_the_death_of_organized_labor.html.
[22] Standard Schaefer, “Who Benef ited from the Tech Bubble: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udson,”CounterPunch , Aug. 29–31, 2003, http://www.counter punch.org/2003/08/29/who-benefited-from-the-tech-bubble-an-interviewwith-michael-hudson/; “Kaysen Sees Corporation Stress on Responsibilities to Society,”The Harvard Crimson ,March 29, 1957,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57/3/29/kaysen-sees-corporation stress-on-responsibilities/; and Gerald Davis, “Managed by the Market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1.
[23] “Life Expectancy by Age,” Information Please, Pearson Education, 2007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005140.html.
[24] Ernest Haveman, “The Task Ahead: How to Take Life Easy,”Life , Feb. 21, 1964.
[25] Pierre Martineau, “Motivation in Advertising: A Summary,” in The Role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57), cited in Fullerton.
[26]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08.
[27] William Shannon, quoted by Richard Rovere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Spring 1962).
[28] “U.S. Federal Spending,” graph, in U.S. Government Spending, http://www.usgovernm entspending.com / spending_chart_1900_2018USp _XXs1li111mcn_F0f_US_Federal_Spending.
[29] Cited in Mary Ann Glendon, “Lost in the Fifties,”First Things 57 (Nov. 1995): 46–49,http://www.leaderu.com/ftissues/ft9511/articles/glendon.html.
[30]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An Internet Resource,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Maslow/motivation.htm.
[31] Cited in Ellen Herman, “The Humanistic Tide,” in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http://publishing.cdlib.org/ucpressebooks/view? docId = ft696nb3n8&chunk.id =d0e5683&toc.depth = 1&toc.id = d0e5683&brand=ucpress.
[32]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49.
[33] Ibid., p. 144.
每年,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都会举行12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在每次调查中,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联系500名消费者,并询问他们对美国经济状况的看法。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50个问题,涵盖了消费体验的方方面面。有些问题是关于消费者对总体经济情况预期的(比如,“你认为现在是购房的好时机吗?” [1] )。也有一些问题更加私人化(比如,“在未来12个月内,你认为你的收入会比去年高还是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反映的是各种意见、经验、启发、焦虑的综合体(这些都是受访者“自我”的体现),最终所有这一切都会被经济学家总结为一个数字,那就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指数在每月中旬公布,是美国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虽然这些受访的民众并不是经济专家,但将他们的答案汇总起来,能可靠地预测未来3~12个月美国的经济表现。对未来经济表现的预测包括很多方面,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到房屋购买情况、零售业销量以及美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或超过85,就意味着美国将迎来良好的经济前景。而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15个点或更多,则说明未来将面临经济萧条。最近几年,上述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保持在70~80,这个水平比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低了许多,但也合理地反映了消费者对经济缓慢恢复的焦虑。
为什么消费者信心指数有如此强大的预测能力?其实这个现象并不奇怪。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70%来自消费者的支出,而在这些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消费者信心影响的非必要性支出。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当然对经济前景有很强的预测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纽约消费者信心指数)都被市场当作神谕一般的指标。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制订其节假日消费预期和生产计划的时候,一定会参考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利率水平和制定其他经济政策的时候,也一定会参考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然,华尔街更是把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作能影响市场走向的数据。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布后的几毫秒内,成千上万只面向消费者的公司的股票就会被买进和卖出,因为交易员(更准确地说是负责交易的超级电脑)争先恐后地想把人们的乐观和焦虑情绪直接转化为资本利得。 [2] 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能够真实地反映消费者的精神状态,那么现在自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在毫秒水平上被度量了。
消费者信心指数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追踪自我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演进。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建于二战刚刚结束时,在指数创立之初的25年中,这一指数长期保持在90~100,这反映了战后的经济繁荣情况和乐观情绪的盛行。然而到了1970年,该指数突然出现了大幅波动。指数一度跌至50出头,虽然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之后又进一步下跌。消费者摇摆不定的情绪反映的是一系列的经济冲击,首先是欧洲和亚洲竞争力量的崛起,接着是原油价格的暴涨,以及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分别发生于1974年和1980年)。仿佛在一夜之间,战后的繁荣化为乌有。收入停滞不前,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主导世界时,美国人民曾拥有过强烈的信心,此时这种信心被全球化经济带来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取代了。
然而,消费者不稳定的情绪不仅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变化,还导致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等保守主义政治家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罗斯福新政中,政府曾对经济进行过大规模的干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转向了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方针。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方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放任经济自由运行。政府政策的核心是给予公司和个人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标志着持续了几十年的政府战略突然改变,然而这种趋势也许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动摇了美国人民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的信心。保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罗斯福新政中的经济管理政策(包括大量政府监管、高税收、对工会的强力支持等措施)使得美国公司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对里根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司和消费者)最大化地追求其个人利益,才可能促进整个社会重新回归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途。
然而,事实发展的方向和政治家的理想并不一样。虽然被解放的美国公司很快就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优胜者,但对于很多普通消费者而言,经济自由的意义却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随着经济革命的结束,普通美国人的财富显著增加,消费者的自我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自由主义推行的那一天开始,“冲动的社会”的趋势再次抬头。
如果我们想把这些崭新的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新时代浓缩成一种人物形象的话,那就是狙击手型的企业家。在战后的商业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是商业帝国的建造者(这些公司的CEO通过科学方法将大量工人有序地组织起来,大规模地生产各种产品)。而在自由市场的新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却变成了狙击手型的企业家,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带有破坏性。“狙击手”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他们在市场上寻找经营不善的、股价低迷的公司,然后悄无声息地买进这些公司的股票,变成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他们的融资手段通常是发行高收益债券,又称垃圾债券)。在成为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以后,“狙击手”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公司重组”。很多时候,所谓的“公司重组”其实意味着对原有组织的大量破坏性行为,这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债券交易者卡尔·伊坎和房地产大鳄维克托·波斯纳。狙击手们会关闭所收购的公司中业绩较差的部门,解雇成百上千的员工,然后将重组后的公司以几千万美元的高价卖出。在另一种情况下,“狙击手”则会将收购公司拆分成许多部分,将其分别出售获取利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数百家公司被收购,这些公司有的被重组,有的则完全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这种收购重组行为无异于一种经济上的暴力,不仅伤害了脆弱的公司,更伤害了公司的员工和依赖公司而生存的社区。上文提到的维克托·波斯纳在收购一些公司后,完全掏空了公司员工的退休基金,用这些钱购买游艇和赛马,支持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狙击手”卡尔·伊坎在收购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以后,以这家经营不善的航空公司的名义借款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他自己的腰包),然后再出售环球航空公司利润最高的航线(这种行为被称为“资产剥离”)来支付这笔巨额债务。这些“狙击手”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沙龙。组织公司收购业务的德崇证券公司每年组织会议,让这些公司重组界大鳄齐聚一堂。这个会议被称作“捕杀者的舞会”。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文化的时代精神为“贪婪是一种美德”。对很多批评家以及在公司并购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这些公司“狙击手”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恶魔。然而对很多保守派经济学家而言,这些公司“狙击手”却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狙击手”之所以选择对某些公司下手,是因为这些公司股价低迷,而股价下降是因为这些公司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随着战后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美国公司变得过于自满、效率低下。它们雇用了太多的员工,把公司的规模铺得太大,根本无法完成精打细算的成本控制工作。正因如此,很多美国公司被外国竞争者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因对经济危机毫无准备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情况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指下降了50%,而这些公司的股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股票贬值一半,却无力扭转这一趋势。因为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几乎没有任何决策权:当时公司的主要决策是由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而当时他们并不重视公司的股价以及股东的利益,他们更看重的因素是劳动力或供应商。从华尔街的角度看,公司“狙击手”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市场化的方法纠正美国公司管理不善的问题。
这种纠正进行得极为迅速。随着一家又一家公司被收购拆分,美国的商业社会陷入了恐慌之中。即使是没有被“狙击手”盯上的公司也想尽一切办法抬高公司股价。很多公司大幅削减成本。更重要的是,公司开始以公司股票代替现金作为付给公司高管的报酬,这种激励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公司高管的战略和行为。以前,公司高管通常把股东当作一群指手画脚、好管闲事的家伙;如今,公司高管自己也成了公司的股东,因此他们有极大的动机尽可能抬高公司股价。这种把抬高公司股价作为终极目标的行为让很多传统的公司管理专家深感不安,然而支持新股东制度的自由市场派学者却为这种行为拍手叫好。这些学者认为,高股价说明公司的经营行为让股票市场觉得满意,并且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正确的。根据所谓的“效率市场假说”,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认真研究上市公司信息的投资者——代表着一种无所不知的最高智慧。这种最高智慧每时每刻都在评估所有公司的优点和弱点,然后通过买卖公司股票告诉大家哪些公司经营得好,哪些公司经营得不好。买入某公司的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上升,卖出某公司的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下降。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效率市场都通过公司股价的变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只有那些能充分领会效率市场的智慧,并根据市场指示来调整自己的公司,才能保持较高的股价,从而获得经营上的成功,而不能适应这种市场智慧的公司将被淘汰。这就是华尔街所说的“股东革命”。
这种达尔文式的经济理念与美国战后盛行的经济哲学完全不同。在战后时代,人们认为公司不仅应该对股东负责任,还应该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公司的员工以及公司所在的社区。然而,如今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种要求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公司并不是一种需要供养各种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机构,而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用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的话来说,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关系的集合”,公司唯一的目的是“最大化股东的价值”。 [3] 这种合同关系的集合对任何人(如公司的员工)都没有义务,就像我们没有义务在某一家特定的副食店买东西一样。 [4] 股东价值学说的支持者认为,正是所谓的社会责任(即公司对员工——或者对社会其他各方——所负的除高效经营之外的任何责任)让很多公司无法实现它们真正的社会责任——实现财富最大化,这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础。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后来被大量引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说:“对公司来说,它们的社会责任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充分参与所有能够提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推广到了公司界。这派经济学家认为,让公司最大化自己的财富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用,而靠政府干预来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只会导致低效率现象的产生。
到20世纪80年代,效率市场和股东价值的逻辑已经拓展为一种政治哲学。市场不仅是公司战略的最佳设计者,甚至成为组织自由社会的最有效方法。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全面结束以及罗纳德·里根的上台,美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与经济文化完全平行的变化,我们远离了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管理理念,投向了自由市场的怀抱。对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其他保守派政治家而言,他们不仅成功废除了许多商业管制条例(如阻止公司收购的条款),而且成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能对经济活动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罗纳德·里根曾经开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玩笑,他说:“在英语中,最可怕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这种对自由市场的崭新信念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法学院和商学院中,股东价值论成了未来商业领导者们的必修课,也成了唯一被认可的正统理论。华盛顿一位劳工方面的说客西尔弗斯曾在哈佛商学院和法学院受过教育,而他在校时正值股东革命发生后不久。西尔弗斯回忆道,他上学的时候,股东价值理论经常与传统的管理理念发生激烈的冲突。他说:“你经常会听到一位教授声称,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关系的集合,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激励机制。然而10分钟以后,同一位教授又会大谈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于是你就会说:‘喂,等一等,这位教授,你不可能同时相信这两种理论吧,它们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啊。’” [5] 然而,随着这批学生逐渐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公司律师,股东价值的理论终于控制了美国的整个商业界,再也没有人对上述矛盾提出质疑了。美国的公司不仅很快习惯了更宽松的监管和失去力量的工会(工会不仅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加入公会的劳动者人数也不断下降),也越来越无视曾经主宰公司管理的很多传统价值。战后的美国公司重视长期稳健的增长,而如今的高管们却片面追求高利润和高股价。因为公司高管的报酬越来越多地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发放,所以如果高管能通过某些战略措施成功抬高公司的利润和股价,就能获得金钱上的丰厚回报。于是,公司的战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采用能够提高公司利润、抬升公司股价的技术。提升利润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成本,于是降低成本成了美国公司的首要经营战略。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界一致认为取悦华尔街、迅速抬升股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宣布公司将大规模裁员。公司与员工终生合作的情谊已经成为过去的传说。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些革命者试图用效率市场学说重塑整个商业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又找到了一种更新的工具。这次的工具不是由华尔街发明的,而是由硅谷发明的。随着这种新工具的引入,股东革命被推上了光速发展的轨道,市场与消费者的自我被空前地拉近,两者似乎已经永恒地融为一体了。冲动的社会即将诞生。
虽然商业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电脑了,但当时电脑技术的成本极为高昂,只有一些规模极大的公司才用得起。然而,随着1972年微处理器的推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很快,一块小小的芯片上就可以有几千个用于存储数据的半导体,能够完成以前只有巨型电脑才能完成的任务。计算速度变得更快了,而成本却只是原来的零头。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英特尔4004——的计算能力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台式计算器。然而随着英特尔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则变成原来的一半。 [6]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摩尔定律的两条指数曲线(一条是指数上升的计算能力,另一条是指数下降的成本,摩尔定律是因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的名字而得名的)使得价格低廉的电脑遍布整个市场。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数字革命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是个人电脑的出现。现在早已过时的软盘和黑屏绿字的显示器在当时却带着无比新奇的荣光。实际上,数字革命对冲动的社会的演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计算成本的大幅下降加速了商业世界与股东利益的融合。现在,在确保公司的经营效率方面,华尔街成为更残酷的执行者。有了电脑和以电脑为基础的数据,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几乎可以实时监控公司的各项表现,快速分析公司的数据,然后通过电脑立刻做出买卖股票的决策。到20世纪80年代,只要公司的季度利润数据令人失望,该公司的股价就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下跌;不久以后,从季报出炉到股价发生波动甚至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电脑也使得公司可以更快地迎合华尔街的需求,从而获得利润。比如,随着以电脑为基础的设计和生产工序的发明,公司能比以前更快地研发新产品,并迅速将新产品投放到市场中,为投资者赢得利润(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一种新车型从开始设计到投放市场的时间从4年减少到18个月)。 [7] 但是,电脑对商业界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成本控制。有了电脑的帮助,生产商可以将很多高度复杂的经营步骤自动化,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大幅提高商品的产量。离岸外包也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旧金山或纽约(或柏林和东京)的工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电脑上进行新产品的设计,然后将设计方案发送给远在墨西哥或中国的工厂,从而享受那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了电脑,现代公司真的成了一种抽象的集合体,能够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快速地集合起来,获得最迅速的高额回报,而这些生产要素的形式和所在地已经不能成为公司获利的障碍。
通过迅速高效地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公司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到20世纪90年代,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的股东回报率(股东回报率包括股价的上升和发给股东的红利 [8] )达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以上,几乎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股东回报率的最高值。 [9] 各大股指一路高涨。每到季度业绩汇报的时候,都会不断传来各种捷报,股东价值的革命和效率市场的逻辑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很多公司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越来越多的公司股票作为报酬,以“激励”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当时,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使与互联网有关的技术股票的股价飙升。对很多专家来说,互联网热潮的兴起标志着新经济秩序的最终确定,他们认为数字技术和市场效率的结合能够在理论上创造比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更多的财富。美国又成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强国。
然而,我们渐渐发现,互联网热潮所带来的财富增加远不像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富增长那样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摆脱了政府干预和社会责任期望的束缚,美国的企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导致企业开始追求一种更高效却更狭隘的繁荣:只考虑股东和公司管理者的利益,把其他相关方完全抛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是我们选择的全新效率市场模式所带来的必然逻辑结果。因为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企业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近乎抽象的存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企业的经营流程试图将投资直接转化为收益,而在这两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低效率元素都已消失殆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冲动的社会的标志是自我与市场的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融合的又一种表现(这一层面上的融合不太直接,因此也较难预见):由于如今的企业可以自由地致力于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企业的行为模式使它不再像是一种社会化的、集体化的机构,而更像是个人的“自我”——这种自私的“自我”完全沉迷于自身的需求与目标之中,而对他人的利益毫不关心。
虽然股东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其他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劳动者)却受到了传统经济周期中从未有过的伤害。在之前的经济萧条中,确实也发生过大规模的裁员现象,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就业岗位的数量也会高速增长。现在,这一规律被打破了。有些工作岗位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中,这在制造业板块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最多稳定的、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制造业是中产阶级存在的基础。然而1979—1983年,至少有200万个工厂工作岗位从美国消失。 [10]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在这轮经济繁荣周期中,这200万个工作岗位非但没有重新出现,反而又有另外46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永远地消失了。 [11]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新兴的信息技术部门的职位,但是技术部门工作机会的增加不能完全补偿制造业萎缩带来的工资损失。美国的中位数收入曾在战后快速且稳定地连续增长了几十年,然而制造业的萎缩导致美国的中位数收入出现了下跌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经历了第一次不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复苏。人们渐渐看清了这样的事实:战后的经济繁荣再也不会回来了。至少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那样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美国人曾经拥有非常稳定的工作保障,如今裁员成了家常便饭。即使是还没有被解雇的员工,很多也变成了合同工。合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更低,工作稳定性更差,升职的机会也更少。工资的增长进入了完全停滞的阶段。1973—1993年,美国家庭的中位数收入在根据通胀因素调整后仅仅增长了7%,而在之前的25年中,美国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曾经翻了一番。 [12] 对中产阶级的工人而言,这种财富增长趋势的变化是残酷的。1973年,一个工资收入中等的30岁美国男性的收入是20年前他父亲收入的160%。而到了1993年,该工人儿子的收入反而比父亲1973年的收入少了25%。美国自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了工资增长停滞,而工资增长是战后经济繁荣的核心,也是我们后物质主义信念背后最重要的基石。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美国收入的下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激烈进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资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劳工运动的衰落。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不仅工会的规模比以前小了,而且工会的权力和效率也明显下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每年发生约300次大型罢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罢工风潮,工会把工人的工资不断推高。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仅发生8次大型罢工,而20世纪90年代总共才发生了34次罢工。 [13] 此外,电脑技术在大幅提高制造业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的重要性:有了电脑的帮助,大型制造商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商品。事实上,由于电脑的成本不断降低,而计算能力却每年都在大幅上升,很多公司发现,通过投资电脑和与电脑相关的机械设备,并降低对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大幅提高公司的利润。 [14] 简言之,技术提供的回报要大于劳动力提供的回报。
工人收入的下降也反映出股东革命后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公司管理文化。当然,成本控制是必要的: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的商业界逐渐变得过于臃肿和懒散。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渐渐习惯了一种效率较低的商业模式:很多公司变成了一种私营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工会没能快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比如国外竞争的加剧),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内部的腐败和低效率问题:即使在劳动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的情况下,有些工会仍然要求雇主定期大幅提高工人工资,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从工人工资下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并不是股东革命的唯一目标。自从有了以公司股票激励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公司管理者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个人财富的欲望已经高涨到了扭曲的状态。因为劳动力成本往往是公司生产成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员工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最大,很多生产过程被外包或自动化,大量劳动者被裁员。除此之外,员工的福利大幅降低,尤其严重的是,对员工的培训投资大幅减少了,这意味着对公司来说员工价值会进一步下降。
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认为,上述现象导致美国商业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拉佐尼克认为,战后美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奉行一种“留存与再投资”的战略,公司每年会自动留存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对公司的投资,投资形式包括建立新的工厂和提高工人工资。然而在股东革命以后,美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变成了“缩小规模与分红”,管理人员尽一切可能缩减各种开支,把省下来的钱发放给股东(包括他们自己),发放形式包括高额分红以及股价的快速增长。 [15] 缩减开支曾被视作应对经济危机和其他特殊经济事件的一种暂时性手段,如今压缩成本成了常态。所有公司都不断地拼命压缩成本,不论经济情况怎样,也不论有没有必要。现在,不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公司的经营者都持续不断地努力缩减开支。拉佐尼克告诉我,股东革命最初可能是一种减少公司浪费、提高公司效率的有益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很快就变了味儿。如今社会普遍认同应该给予公司高管最大限度的自由,于是公司高管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员,或者进行其他以前因为政治因素而难以实施的改变,并可以迅速从中获得高额的个人收益”。 [16] 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CEO的年薪可以达到100万美元。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很多公司将公司股票的期权作为高管薪酬的一部分,很多CEO一年可以收入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
由于美国政界普遍接受了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尽管公司高管的薪酬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大部分决策者却认为这样的薪酬是合理的。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自由市场愿意支付的任何水平的薪酬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市场对这样的薪酬水平也很宽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被公司股票所激励的高管愿意为保持公司的高股价做任何事情。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受赞美最多的公司高管恐怕要数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1981—1985年,杰克·韦尔奇总计裁减了通用电气的10万多个工作岗位,因此获得了“中子弹杰克”的“美称”。 [17]
这标志着美国的公司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一家典型的美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像国家一样运行的,公司拥有自己的“国家主义”传统和价值观,员工为公司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同时也对雇主怀有强烈的归属感,这些都是当时公司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劳动者和管理层经常发生冲突和斗争的行业中,大家也普遍认同管理层与劳动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离不开另外一方。然而,根据新的企业文化,公司再也不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大家庭了。员工越来越认为管理者是一群冷酷自私的家伙,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个人收入最大化可以随时抛弃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劳动者的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美国公司把不断快速压低成本和抬高公司股价作为商业战略的核心时,管理者不可避免地会像热气球驾驶员对待压舱物那样对待他们的员工:扔掉的压舱物越多,他们自己就会飞得越高。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经济安全感持续下降,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持续的政治反抗。长期主管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工作的理查德·柯廷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出现下行趋势,这立刻激起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抗议。经历了几十年的战后经济繁荣,美国人“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共同价值,并且总是将一切问题怪罪在政府身上”。 [18] 显然,里根对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压倒性胜利无疑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抗议。当时,美国民众强烈反对延续战后的罗斯福新政,而是支持一种理想化的自由资本主义方针,并支持个人经济自由的最大化(尽管这样的政策存在一些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虽然自由资本主义和效率市场政策并未再创战后的经济繁荣,甚至还导致美国的经济情况出现进一步恶化,但美国选民却表现得出奇地平静。
选民的平静部分是由劳工运动的衰落造成的。由于劳动者的政治权力下降,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支持新的经济政策了。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了选民的平静。其中之一显然是因为很多美国人确实享受到了里根经济政策的好处。20世纪80年代,对收入较高的美国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和财富都出现了稳定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税率的降低和股票市场的繁荣。美国的上层阶级与其他民众的差距开始拉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
然而,即使在美国的中下阶层中,仍有很多人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方针。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马斯洛和英格莱哈特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战后的经济繁荣让美国人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以及更好的社会。随着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美国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仍比他们的祖辈富裕许多;另一方面,财富增长的趋势已经停止,人们不能期望美国经济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高速增长了。很多美国人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特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把这种状态称为“不安全的富裕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大部分物质需求已经被满足,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却无法继续被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对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对更多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其他后物质主义的抱负。这让公众普遍感到愤怒、焦虑,同时很想找出应该为这种失败负责的人。20年前,公众也曾感受过同样的愤怒和焦虑,但当时这种愤怒和焦虑促使民众采取了政治上的行动,而目前的文化却把民众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对很多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失败与过剩导致集体主义价值观受损。甚至连很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都认为,罗斯福新政之下的大量社会福利和社会的大幅扩张事实上削弱了国家实力。 [19] 于是,很多人倒向经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镀金时代的纸醉金迷再次成为人们迷恋的目标,民众日益认为个人的财富与国家和集体无关,主要来自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在全球化、数字化、股东价值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多时候并不能带来成功。然而,这一悖论无法抹去自由资本主义传递给公众的强烈信念:或迟或早,美国的黎明终会来临。
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也稀释了美国民众的愤怒和焦虑。虽然在自由市场的政策下,很多美国人的个人财富缩水了,但自由市场却向他们提供了获得自我满足的其他方式。随着电脑技术的高度发展,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售价都大幅降低。1970—1989年,美国耐用商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26%。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大幅下跌,每磅鸡肉的价格变成了过去的1/2,一个麦当劳芝士汉堡的价格比过去低了40%。消费成本变得如此低廉,限制人们消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二战”之前,节俭曾被美国人视作重要的美德,这种价值观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期间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但是随着消费品价格的降低和极度丰富的商品产量,美国人终于完全抛弃了节俭的观念。用科技作家克里斯·安德森的话说:“低廉的物价和丰富的商品教会我们如何浪费资源,也教会我们忽略关于成本和物质稀缺性的本能。” [20]
电脑技术不仅让消费变得更便宜,也让消费的过程变得更有趣。电脑化的集中生产线使商家可以快速完成产品的转化:一家工厂就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的产品,也可以更频繁地更新产品的型号。电脑化的供应链和物资仓储系统使得像沃尔玛和塔吉特这样的零售商可以轻松地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商品种类。因为商品种类的增加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商家在利润驱使下又会制造出更多种类的商品,如此不断循环。在20世纪50年代,一家典型的美国超市通常会出售3 000种不同的商品,即3 000种不同的库存量单位(SKU), [21] 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以前的10倍(沃尔玛等某些大型超市甚至可以同时出售10万种不同的商品)。 [22] 从汽车到服装,再到室内装饰和音乐,摩尔定律不仅促进了电脑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也促进了商品种类的指数级增长。消费者面对着几乎无限的商品选择,于是消费变成了一件完全个人化的事:每个人都可以从无数种商品和服务中选择,从而获得完全符合个人品位的消费体验。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随着录像机的发明,我们再也没有必要观看和其他人相似的东西了。不管我们想看什么,一定可以从音像店租到完全符合我们需求的录像带:艺术电影、浪漫喜剧、日本动漫、恐怖片、血腥片、色情片(随着录像技术的发展,制作色情片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色情业每周能产出150部新片)。 [23] 20世纪8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影片以录像带的形式发行,录像带的销售和租赁收入超过了电影的票房收入。 [24] 在其他消费品领域,同样发生着这样的故事。据新学院大学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的杰夫·马德里克估计,1970—1995年,美国每年的总消费商品种类增加了10倍。用马德里克的话说,大部分西方后工业化国家都进入了“消费者选择的时代”。
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经济与自我之间,形成了正反馈的循环,把消费主义的热潮进一步推向高峰。虽然我们无法继续改善个人的经济状况,却可以继续保持战后自我提高和自我发现的潮流。这个潮流的开端是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个人探索,现在这种探索已经完全被工业化和专业化了,变成整个社会的大型文化运动。我们重新装修房屋,让室内设计完全符合我们的内在情感。我们通过山达基教、超在禅定法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来追求内心的完善。健身和形体塑造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是运动员和军事教练员的专利,如今却变成世俗宗教的核心。1970—1990年,美国参加慢跑活动的公众数量从大约10万人 [25] 增加到3 000万人。 [26] 成千上万的健身房、体育用品店和产品目录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从跑鞋到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从动感单车到跑步机,从一般健身中心到有氧健身法,从蛋白粉到碳水化合物负荷法,从心率监测仪到训练专用食品),这些商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系列提高生产率的工具,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继续追求自我完善的目标。
电脑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自我发现过程更加便捷高效,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让我们能够更轻松地支付自我发现的开销。有了以电脑为基础的信用分数,银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贷款决策,向消费者发放信用卡。以前这个过程通常至少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金融方面的创新远不止如此,因为电脑使银行能够轻松地按照信用分数、收入及其他个人数据对消费者进行分类,不断增加的个人债务被银行打包成各种证券,卖给华尔街的投资人,立刻获得巨额的利润。现在,银行不仅有更强的动机向个人消费者发放贷款,也有更多的额外资本作为贷款的资金来源,因为通过销售债券化的贷款获得的现金又可以被再次用于贷款发放,而新的贷款又可以被再次证券化,如此不断循环。随着信贷供给的增加,利率变得很低,银行业传统盈利业务的利润收窄。为了抵消这方面的负面影响,满足华尔街所追求的高额回报率,银行采取了薄利多销的业务模型。消费者信贷和其他消费者产品一样,被包装成各种创新性的、充满野心的市场宣传计划进行推广。银行所提供的贷款种类几乎已经涵盖了任何你能想象到的领域: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房屋装修贷款、大学教育贷款、度假贷款、游艇贷款,你甚至可以通过贷款来还债,或者贷款进行整容手术。银行提供的信贷越多,消费者花的钱也就越多。随着全球化进程、技术革新以及新的商业战略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收入也许已经无法快速增长,然而我们的购买力仍然能够继续高速攀升。当然这样的特权同样是拜股东价值革命和数字革命所赐。一时间,美国公众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战后的经济繁荣时代真的又回来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业的双重创新把美国经济推向了又一个繁荣的周期,美国人不仅重新开始了自我发现和自我身份创造的征途,并且把上述追求的强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杨百翰大学的社会学家拉尔夫·布朗专门从事商业社会学研究,他认为,除了社会底层最穷的美国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美国人都已经习惯了通过消费来获得个人的身份,这种追求自我的途径如此高效,几乎变成了美国人的第二本能。拉尔夫·布朗说:“只要我们渴望在生命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得到它。我们也许只要花费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通过消费获得一种自我身份。这样做变得越来越简单,购买自我身份的效率也越来越高,这种高效本身已经变成美国人自我的一部分。” [27]
显然,我们不得不开始担忧这种高效率是否能维持下去。1987年,由于电脑化的信贷条件过于宽松而产生的信贷泡沫终于破灭,泡沫的破灭导致股市崩盘,而电脑化的股票交易系统又进一步造成美国股市的完全失控。显然,高科技市场存在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风险。一位经验丰富的股票经纪人这样对我说:“我们进行了这么多创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创新加总起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技术将把我们带向何处。” [28] 同时,对消费者来说,虽然最新的经济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诱惑,却并没有真正重塑我们的经济安全。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但美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率(每年2.3%)只相当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2/3。 [29]
然而,不管经济情况如何,美国人已经无法停止追求自我满足的步伐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不仅是金融方面的债务,还包括社会、心理,甚至生理方面的债务。虽然我们更加迷恋健身和运动,身材却不断变得更加肥胖。我们每年消费大量的镇静剂和抗抑郁药物。自我提高的欲望空前强烈,以至大部分美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很多批评家认为,追求自我曾经意味着自我价值的提升,意味着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意味着在人格上更成熟、更具有马斯洛所说的“民主化特征”,而如今对自我的追求已经变成了自我沉迷和自我孤立,反而导致人们远离社会化的生活。作家皮特·马林曾经写道,现在所谓的“自我提高”已经完全变味,成为“脱离人类历史与道德,否认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互惠互利原则”的代名词。 [30]
倒退成为一种常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逃离城市风潮,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社会撤退的运动。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其他“创造阶级”成员——几十年前这些人曾是进步运动的核心,曾为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出现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抛弃了理想主义的追求,隐居于物质世界的海洋中。这群人如今追求的是新潮的社区、私立学校,甚至策略婚姻:和比自己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结婚或社交的情况越来越少见了。克里斯托弗·拉希抱怨说:“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自己从公众生活中移除了。” [31] 即使是对那些继续过公众生活的人来说,对自我的更多关注也导致团结和社区等传统价值观面临压力,对个人自由的更高期待导致集体性的、相互性的行为越来越稀少。很多社会批评家都认为这样的趋势令人担忧。作为城市社会演进过程的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艾伦·埃伦霍尔特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警告:“隐私、个人主义以及越来越多的选择并不是免费的,如果社会不对这些行为加以限制,就一定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2]
20世纪90年代,冷漠成为美国社会的通病。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经写过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书名为《独自打保龄球》。在该书中,普特南认为美国民众正日益远离公共活动,他为这种“社会资本”的流失而哀叹。美国人不仅投票率下降了,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也越来越低。做志愿者的人减少了,给请愿书签名的人减少了,写给国会的抗议信少了,看政治新闻的人少了,去教堂的人少了,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和会议的人也减少了,甚至人们去邻居家串门的次数和每个人拥有的亲密朋友也减少了,唯一保持增长的是物质主义的倾向:1965—1995年,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把致富作为人生首要目标的人数比例从50%上升到了75%以上。 [33]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毫不掩饰的物质主义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今体育明星变成了拥有自由经纪人的百万富翁。摇滚音乐人和作家一夜之间告别低调,尽情享受财富和名誉的光环。在商业世界中,人们甚至不屑再用高尚的商业道德标准作掩护,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商业狙击手和套利交易专家每年的收入可以高达上亿美元。美国企业中CEO的平均收入是劳动者中位数收入的100倍以上(20年前只有20倍)。 [34] 镀金时代再次回归,而那个时代的改革者们的努力似乎完全白费了。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根本无暇质疑这种新战略的可持续性,也无暇关心现在的消费者文化究竟能否长期发展下去。我们的注意力被另一轮个人权力的飙升夺走了,而这一轮新的革命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推向气吞山河的新高峰。
在这轮新的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偶像人物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史蒂夫·乔布斯。1984年1月,乔布斯留着披头士乐队式的发型,穿着整洁漂亮的黑色西服,向一群鸦雀无声地坐在台下的苹果股东推出了苹果的麦金塔电脑。早在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就已经面世了,但是麦金塔是第一款真的满足了一般用户对尺寸和功能的需求的电脑,这一机型的成功将完全改变我们的世界。即使今天再回头去看这场1984年的麦金塔发布会(这个视频在网上随处可以找到),我们仍然会被这款机型的新颖所震惊:麦金塔电脑体积非常小,配有一款不断闪烁的黑白显示器,看到这款机型的时候,台下的人群仿佛触了电一样。当时,电脑行业以外的人几乎从没见过电脑屏幕上出现图形,靠鼠标点击、拖拽运行的“用户界面”更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当时的人们还在DOS系统下靠手工打字输入命令。也没有任何人见过能让用户在电脑上画画或者改变字体的软件。麦金塔电脑甚至还通过一段事先录好的独白对乔布斯和观众讲话,虽然这番演说带有一种奇怪的电子口音(说不定这种口音正是引起公众注意的关键因素),但麦金塔仍然立刻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人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技术,虽然这种技术当时只具雏形,却有着魔术一般的魅力,因为它可以向我们提供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个人权力,即使是在战后经济繁荣的顶峰,也从未有人拥有过这样的个人权力。随着这种技术的出现,欲望和拥有之间的距离,即“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之间的距离迅速向零靠近。
在互联网世界中,上述距离真的完全为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乔布斯这种点击操作的创举已成长为完整的用户平台。搜索引擎、电子公告牌、聊天室几乎瞬时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拥有无限丰富的信息、互动和体验,从最小众的爱好到各种人类可能想象出的色情图片,再到政治不正确的讨论组,以及对新闻、体育、天气的数不清的分析与评论——只要是人类能想到的东西,网络世界里几乎都有。
至此,我们终于建成了新的经济范式,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回答了我们所有深层次的焦虑,这种新的经济范式似乎穿越了旧经济秩序的一切限制和不平等。随着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消费过程变得极度压缩与高效。也许我们的经济仍然充满了波动与不确定性——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美国战后的信心与稳定感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繁华旧梦。但是,个人消费者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去追求一切他想要的东西。现在,人们可以购买任何地方的东西,在任何地方工作,与任何地方的人交流,我们越来越少地依赖传统的生产系统,也越来越无须遵从专家与权威的意见。在数字革命的浪潮下,从前对社会起关键作用的各种中介服务(包括旅游经纪人、电话接线员、编辑和出版商)迅速变得多余了。甚至连金融市场也更大规模地开放了。到了世纪之交,已经有700万人参与网络交易,通过数字的力量(如玛丽亚·巴蒂罗莫和吉姆·克莱默等金融大师的神圣建议)打破更多个人权力的界限。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金钱甜心”巴蒂罗莫曾在2000年对她的观众说:“这已经不再是一场职业的游戏了。个人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普通人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了。” [35]
虽然上面的说法可能有一点夸张,但这些文字很好地描述了那个时刻美国奇怪的乐观主义:虽然经济上的安全感在不断降低,但民众却相信我们可以继续追求并获得更多的个人权力,这种信念变成了我们的信仰,缓解了一切经济上的焦虑。确实,随着网速的提高和信息效率的进步,我们迎来了一轮又一轮更快的满足机制,我们的预期和态度也随着这些技术的变化不断加速。我们很快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竟然曾经容忍过实体市场所带来的延迟和不便,我们甚至忘记了实体市场曾被我们视作是先进的、充满优越性的;我们不仅越来越多地期望更快速的自我满足,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网络世界中,而且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对可能性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只要我们对目前的任何东西有任何不满,我们就会坚信某种新的产品、体验或者互动(一种能够进一步缩小欲望和拥有、欲望和存在之间距离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人们对于史蒂夫·乔布斯及其玩具般的产品的欢呼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麦金塔的发布会上,我们都瞥见了一种权力和自由,这种权力和自由很快就会被每一个个体所拥有。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于这个新的时代。
[1] “Survey of Consu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http://www.sca.isr.umich.edu/fetchdoc.php?docid=24776.
[2] 2012年,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新闻媒体透露,自2009年以来,该指数在向市场发布之前,每次都被提前两秒透露给某些组织的高频交易员,此举让这些金融机构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
[3] 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research paper, http:// www.sfu.ca/~wainwrig/Econ400/jensen-meckling.pdf.
[4] 经济学家阿门·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曾这样说:“我并没有在某家副食店买东西的合同义务,雇主和雇员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要求他们永远保持雇佣关系。”
[5] Interview with author.
[6] Gary Hector and Carrie Gottlieb, “The U.S. Chipmakers’ Shaky Comeback,” CNNMoney,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1988/06/20/70690/index.htm.
[7] “GM Speeds Time to Market through Blistering Fast Processors,” FreeLibrary,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GM+speeds+time+to+market+ through+blistering+fast+process ors%3a+General..-a0122319616.
[8] 红利是指公司定期从利润中拿出来支付给股东的部分。
[9] “S&P 500: Total and Inf lation-Adjusted Historical Returns,” Simple Stock Investing,http://www.simplestockinvesting.com/SP500-historical-real-total- returns.htm.
[10] William Lazonick and Mary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conomy and Society 29, no. 1 (Feb. 2000): 19.
[11] Ibid.
[12] Ted Nordhaus and Michael Shellenberger, Break 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 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 p. 156.
[13] “Work Stoppages Falling,” graph,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old.post-gazette.com/pg/images/201302/20130212work_stoppage600.png.
[14] 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Declining Labor Shares and 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s,” research paper, October 2012, http:// econ.sciences-po.fr/sites/default/f iles/f ile/cbenard/brent_neiman_LabShare.pdf.
[15] William Lazonick, “Reforming the Financialized Corporation,” http://www.employment policy.org/sites/www.employmentpolicy.org/f iles/Lazonick%20Reforming%20the%20 Financialized%20Corporation%2020110130%20(2).pdf.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William Lazonick, April 15, 2013.
[17] Gerald Davis,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0–91.
[18] Interview with author.
[19] 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民众的乐观情绪,甚至连美国的左翼人士也不再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行的意识形态。
[20] “The Rise of Freakonomics,” Wired, Nov. 26, 2006, http://www.longtail.com/the_long_ tail/2006/11/the_rise_of_fre.html.
[21]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od and Drink , edited by Andrew F.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6.
[22] “Supply Chain News: Will Large Retailers Help Manufacturers Drive Out Supply Chain Complexity?” Supply Chain Digest, June 30, 2009, http://www.scdigest.com/assets/On_ Target/09-06-30-2.php
[23] Robert Peters, “Chronology of Video Pornography: Near Demise and Subsequent Growth,” Morality in Media, http://66.210.33.157/mim/full_article.php?article_no=175;and Tony Schwartz, “The TV Pornography Boom,” Sept. 13,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9/13/magazine/the-tv-pornography-boom.html?pagewanted=all.
[24] Press release, “Industry History: A History of Home Video and Video Game Retailing,”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3, http://www.entmerch.org/press-room/industry-history.html. Accessed February 3, 2014.
[25] “‘Father of Aerobics,’ Kenneth Cooper, MD, MPH to Receive Healthy Cup Award from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ess release, April 16, 2008, http://www.hsph.harvard.edu/news/press-releases/2008-releases/aerobics-kenneth-cooper-to-receive harvard-healthy-cup-award.html.
[26] J. D. Reed, “America Wakes Up,”Time , Nov. 16, 1981, http://www.time.com/time/subscriber/printout/0,8816,950613,00.html.
[2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5, 2012.
[28] Kurt Eichenwald with John Markoff, “Wall Street’s Souped-up Computers,”New York Times , Oct. 16, 1988, http://www.nytimes.com/1988/10/16/business/wall-street-s-souped up-computers.html.
[29] Dean Baker, “The Run-up in Home Prices: Is It Real or Is It Another Bubble?” brief ing paper,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ugust 2002,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housing_2002_08.pdf; and Dean Baker, “The Productivity to Paycheck Gap: What the Data Show,” brief ing paper, April 2007,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growth_failure_2007_04.pdf.
[30] Peter Marin, “The New Narcissism,” Harper’s, October 1975.
[31] Quoted in book review by Scott London, http://www.scottlondon.com/reviews/lasch.html.
[32] Glendon, “Lost in the Fifties.”
[33] All in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except visiting and close conf idants, which is from McKibben, Bill. “Money ≠ Happiness. QED.”Mother Jones , March/April 2007,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07/03/reversal-fortune?page=3Issue.
[34] Ibid.
[35] Charles Fishman,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elevised (on CNBC),” FastCompany,http://www.fastcompany.com/39859/revolution-will-be-tele- vised-cnbc.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第二波数字革命浪潮把科技市场推向新的高峰,芝加哥大学的一位行为学家迪利普·索曼开始研究数字革命中的一项新技术——消费者信贷——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索曼出生于印度,曾经是一名工程师,美国消费者对信用卡债务轻松随意的态度激起了索曼的好奇心,于是他为了研究消费者行为而搬到了芝加哥。美国消费者不仅用信用卡支付各种日常购物款项(这在印度根本闻所未闻),而且很多消费者长期负有大量信用卡债务,因此每月要支付高昂的信用卡利息。美国消费者的这种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然而,在美国,这是一种常态。索曼观察到,甚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的很多同事也同样欠着大量信用卡债务——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经济系学者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每个消费者都当作超级理性的决策者。索曼说,然而当决策涉及他们自己对消费者信贷的应用时,就连这方面的专家似乎也失去了理性,而被“另一种更加强烈的动机所驱动”。
索曼怀疑消费者大脑中的某些功能导致大家不能用对待现金的态度来对待信贷,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他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来测试使用现金与信用卡的区别。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索曼要求两组被试分别用信用卡和现金支付一些虚构的家庭账单,两组被试支付账单的数额是一样的。在支付完账单后,索曼向两组被试提供支出450美元度假的机会。索曼发现,虽然两组被试所支付的家庭账单数额一模一样,但是用信用卡支付账单的被试比用现金支付账单的被试更愿意在度假上花钱,前者在度假上的花费几乎是后者的2倍。在后续的一项实验中,索曼又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索曼在芝加哥大学的书店门外蹲守了3天,并询问从书店走出来的消费者是否记得在书店里购物所花费的具体金额。在记录受访人的答案以后,索曼将消费者回忆的金额与他们手中的收据进行对比。实验的结果非常有趣。在用现金、支票或借记卡付账的消费者中,有2/3的消费者能够准确地回忆起支出的具体金额,另外1/3的消费者对购物金额的回忆虽然有误差,但误差在3美元以内。而那些用信用卡付款的消费者,虽然离他们刷卡消费的时间还不到10分钟,却只有1/3的消费者对购物金额的记忆误差小于1美元。另外有1/3的消费者记忆中的购物金额比实际金额低15%~20%。还有1/3的消费者根本不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如今就职于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索曼这样告诉我:“这个实验的结果让我恍然大悟。原来长期用信用卡购物的消费者根本就不会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 [1]
为什么消费者会记不住信用卡购物的支出金额?确切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有些研究者怀疑,信用卡支出所产生的“痛苦”会延迟传递到大脑,因此消费者对购物细节的记忆会比较模糊。不管具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研究的结果都显示消费者对信用卡购物存在一种反复出现的认知偏差:信用卡让我们摆脱了花钱的内疚感。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用信用卡购物的人比用现金购物的人花钱更多。刷信用卡的人给小费更慷慨,拍卖竞价时喊价更高。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即使不让消费者真的使用信用卡,只要付账时让他们看到万事达卡或维萨卡的标志,就足以刺激消费者花更多的钱。似乎对人类的大脑来说,信用卡支出会让我们计算金钱的程序出现故障。虽然我们试图克服这样的错误,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作为一种刺激消费的“工具”,近几十年来消费者信贷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不仅数量变得更多,而且消费者获得信贷也变得更容易了。现在我们几乎想不出还有任何交易不能用信用卡支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在计算金钱方面的这种思维漏洞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早在索曼进行上述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无力偿还信用卡债务的现象就已经十分普遍了。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个消费者所欠的信用卡债务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3倍。 [2] 家庭债务的增长率比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快25%。(15年前这两个数据的增长率还是一致的。 [3] )个人破产的概率也变成了以前的3倍。 [4]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些情况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比如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的下降,或者金融机构恶意放贷行为的增加。但面对上述研究结果,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高科技消费者经济是否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了过高的个人权力,而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理性地使用这些权力?我们是否已经跨越了某种神经学方面的经济极限?
上述可能性的存在令我们尴尬,然而这种可能性反映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唯利是图的商业模式以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后工业化经济向消费者提供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虽然我们不得不放弃战后社会的经济安全感,但作为补偿,我们却拥有了一种更吸引人的新能力——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自我发现和身份追求。为此,商家向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渠道,包括更廉价的、更快速的食品,更强大的汽车,24小时不间断的娱乐场所,以及非常容易获得的个人信贷。
然而,没过多久,这桩美事就变得越来越像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我发现已经变成了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满足的狂欢。我们的消费支出达到了天文数字。我们的肥胖率不断攀升(1970—1995年,美国成年人中超重的人群比例从3/20飙升到3/10)。吸毒、滥交、出轨者的比例都在不断攀升。在美国,过度的不仅仅是消费。人们的耐心、教养以及自制力似乎都严重缺乏。我们开起车来速度更快,态度更蛮横了。政治领域的党派分化更加严重,更加充满敌意。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疯狂地互相伤害。随着美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实现,社区、邻里、社会等纽带都变得越来越弱。我们追求的所谓自我似乎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讨厌小孩,总是冲动行事,不愿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现象的成因是文化的腐蚀:曾经对我们内心孩子般的自我起限制作用的传统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慢慢腐蚀了,而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科学和宗教领域都导致了追求即时自我满足的倾向。但随着研究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发现这种现象背后还存在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自我权力意识的苏醒。简而言之,消费者经济给予个人太多赤裸裸的权力,于是在追求完美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不可能保持适度,而必然走向过火的境界。
现代化的个人权力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并不是一种很激进的观点。我们的大脑习惯了史前那种物质稀缺的、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因此,当我们面对后工业化和后物质主义的社会时,相对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确定性的增加必然给我们的思维带来一些挑战。然而,即便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古老的生理功能和当代现实之间的错配仍让我们感到震惊,这种错配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惊人的。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涉及我们对“跨期选择”问题的决策。所谓“跨期选择”,是指那些我们必须对现在和未来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做出的决策。比如,我们是应该今天把钱花掉,还是把钱存起来为退休做准备?我们是应该现在忍受辛苦、努力锻炼,还是宁愿日后心脏病发、英年早逝?我们是在圣诞节派对上和同事调情,还是为了享受未来30年婚姻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而克制这种冲动?这类跨期选择问题是我们最常面对的个人选择,也是最重要的个人选择类型之一。跨期选择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健康、理财,到一些集体性的抉择——比如国家负债水平、医疗改革以及气候变化。不幸的是,跨期选择也是我们最容易出错的决策领域之一。在这方面,我们三番五次地犯错误,即使我们明明知道短暂的满足会带来长期的痛苦,我们也常常无法抗拒即时奖励的诱惑(或者试图推迟即时惩罚)。整部人类历史充满了错误的跨期选择所带来的各种灾难。
为什么跨期选择对我们来说如此困难呢?1980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塞勒认为,要想用理性的方式理解人类在跨期选择方面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就必须这样设想:人类的大脑不是一个决策整体,而是两种同时存在的自我的联合体。塞勒将其中的一个自我称为“短视的冲动者”,这个自我只想获得快速的、高效的即时满足。而另一个自我则是“长远的计划者”,这个自我的任务是管理(或者说试图管理)“短视的冲动者”。当时,塞勒并不认为人类的大脑中真的存在这样两个不同的生理部分。他的这种说法带有比喻的意思:我们的决策过程就仿佛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自我一般,他们会在同一时间点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导致我们做出非理性的错误决策。 [5]
塞勒的这种双重自我模型为他招来了很多攻击。虽然这种理论并不是全新的——弗洛伊德也曾提出过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甚至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曾在他的著作中描述过“激情”与“公正的旁观者”之间的冲突。 [6] 然而在塞勒的时代,这种双重自我模型却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猛烈攻击的靶子。因为当时的经济学界主要由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控制,而该理论的核心正是每个人的理性选择特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假设每个个体都会认真权衡所有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以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理性的世界中,塞勒的理论当然被当作一种离经叛道的亵渎。整个效率市场理论成立的基础就是市场中的所有行为体都必须是理性人,都不会明知不合理还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如果这种理性假设不成立,市场就不再是人类智慧的总和。因此,塞勒的双重自我模型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塞勒告诉我,迈克尔·詹森曾公开指责塞勒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7] 迈克尔·詹森曾经是塞勒的同事,也是自由市场理论的支持者。后来,塞勒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职期间,该系一位与理性市场理论渊源颇深的诺贝尔奖得主居然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拒绝与塞勒说话。 [8]
然而,事实证明塞勒的理论是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脑扫描等最新医学技术开始向我们揭示人类决策过程的生理基础:事实上,我们做决策时,确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进行激烈的对抗。这场对决的一方是一种高级认知过程,主导这一过程的是大脑的前额皮质。前额皮质属于人类大脑相对现代的结构,负责抽象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这场对决的另一方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心理过程,掌控这一过程的部分主要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又称“蜥蜴脑”。蜥蜴脑主要负责控制人类对危险、性行为以及其他与生存紧密相关的活动。前额皮质和蜥蜴脑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一对完全不匹配的对手,这两部分不仅决策的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感知和不能感知的事物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前额皮质明白今天的疯狂消费或者婚外恋会导致一个月以后的高额成本,然而我们的蜥蜴脑完全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因为蜥蜴脑在进化上主要负责处理眼前的危机情况,比如战或逃,因此这一系统完全不考虑当下的危险以外的任何情况,“未来”完全处于蜥蜴脑的盲区之中。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一项著名的大脑扫描研究显示,当实验对象接受即时奖励时,他们大脑的边缘区域高亮,也就是说这一区域产生了大量的神经活动。而当研究者向实验对象承诺未来给予他们某些奖励时,实验对象的大脑边缘区域完全不亮。对人类的蜥蜴脑来说,“未来”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
蜥蜴脑的这种“未来”盲区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生理特点是自我与市场矛盾的核心基础之一。因为大脑的边缘系统在人类的冲动行为方面起决定作用。当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大脑的边缘系统会立刻启动一系列强有力的神经活动,促使我们快速行动。大脑的边缘系统可以释放多种神经递质,比如刺激冲动的去甲肾上腺素,以及产生快感的多巴胺(可卡因之所以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冲动,原因之一就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和释放)。 [9] 此外,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还能够通过调控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填满奶油的甜甜圈时,大脑边缘系统只需要几毫秒就能让我们的脑中充满“爱慕”的情绪——想吃甜甜圈的欲望。这种情绪让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想采取行动,甚至理性化的前额皮质也会在大脑边缘系统的影响下放弃对成本的核算,转而追求即时的满足。当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呼唤我们行动时,前额皮质通常会不自主地产生一些与上述冲动相关的思考,这种思考通常都支持我们做出冲动的行为(比如“我今天工作很辛苦,我应该吃个甜甜圈”)。这种不自主的思考通常就是我们的直觉或者“内心的声音” [10] 。换句话说,只需几秒钟,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就能改变我们的心理和神经系统,让我们追求各种短期的目标:从吃甜甜圈到对不守交通规则的摩托车驾驶员大喊大叫,虽然这些短期目标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正常行为模式。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勒文施泰因曾这样写道: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可以“将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人”。 [11]
当然,负责理性决策的大脑部分——前额皮质也有自己的功能。前额皮质能够提出相反的论点,并产生负面的情绪(比如羞耻感)来阻挠大脑边缘系统的行动。但大脑边缘系统的反应是非常迅速和高效的,在这一点上,前额皮质存在巨大的劣势。要想阻止追求即时满足的冲动,前额皮质不仅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观点(比如“甜甜圈会让我发胖”),还需要在提出这些论点的同时制造足够的情绪冲动。前额皮质制造的情绪冲动会与大脑边缘系统制造的情绪冲动互相竞争,看谁能赢得意识的认同。勒文施泰因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的事情(比如收到信用卡账单的痛苦,或者拥有完美的形体所产生的快乐)常常无法转化成此时此地的强大情绪。有时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对未来的情况做出明确的判断。有时情况过于复杂,超乎想象,或者未来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导致我们无法理解未来的后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未来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可触及”的。而勒文施泰因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前额皮质常常不能产生足够强烈的情绪冲动,以对抗大脑边缘区域强有力的野性呼唤。
这种不平等的角力导致我们长期被大脑边缘系统的短视所控制。因为大脑边缘系统在表达欲望方面占支配地位,我们对即时选择(不管是快感还是成本)的感受总是非常强烈的,而对未来选择(比如风险)的感受则比较微弱和模糊。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阿瑟·皮古曾这样说道:当我们考虑未来的情况时,我们好像是把望远镜拿反了,越远处的东西看起来就越小。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价值总会进行“贴现”折算,由于贴现率如此之高,未来的奖励必须比现实的收益大出许多,我们才可能放弃眼前的利益而选择追求长期目标。我们在心理学实验中发现,被试常常会选择眼前的微小奖励,而放弃较大的延迟奖励(比如几周后寄到的亚马逊礼品卡)。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大脑扫描研究论文中,即使向被试提供每周5%或每年250%的收益,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延迟的奖励。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萨姆·麦克卢尔告诉我:“这实在太荒谬了。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能向你提供每周1%的收益,你很快就发财了。”然而,这种非常荒谬的贴现率却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思维上的漏洞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断做出各种错误的跨期选择。
消费者信贷产品就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这种思维漏洞。对由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的“短视冲动者”而言,用信用卡购物只意味着当下的快感和即时满足,而没有任何成本。 [12] 事实上,用信用卡消费当然不是没有成本的。30天后收到信用卡账单时,我们会感到痛苦。而随着未支付的信用卡债务产生利息和罚金,我们的痛苦将会不断放大。然而对“短视的冲动者”而言,这些未来的惩罚都是不存在的。虽然我们的前额皮质能够预见到这种未来的痛苦,但是“理性计划者”缺乏将未来的痛苦变成强烈的当下刺激的能力——用勒文施泰因的话来说,前额皮质没有办法将这种痛苦“现时化”,因此也就无法赢得与大脑边缘系统的战争。于是,虽然明知无力承担这些消费,我们还是会将3 000美元的宽屏电视机或者4万美元的皮卡刷卡买回家。我们的短视行为远远不止滥用信用卡。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明知未来的成本很高,却仍然无法抗拒即时快感的诱惑。(因此我们吃下了汉堡王的三层芝士汉堡,喝下了第四杯红酒,因为某个人的一个眼神而违背了婚姻的誓约。)如果冲动的社会有国旗的话,那么最恰当的国旗图案就是一个反拿望远镜,从错误的一端看向远方的人。
显然,在人类的历史中,这种对未来进行贴现处理的做法曾经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远古的祖先是不折不扣地活在当下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当下奔向另一个当下,不断追逐着粮草和猎物(这些东西被很快吃掉,然后来不及完全消化就排出了体外),不断为了领土和异性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中,只看当下是唯一合理的生存策略,只有为当下拼尽全力的人才可能继续活下去,才可能拥有未来。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有能力克服人类这种天然的短视倾向。随着长期计划变得越来越必要(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逐渐改变了获取食物的战略,转向农耕等需要耐心和长期计划的生活方式),人类发明了各种外在的、社会化的手段来克制我们本能的冲动。各种社会化限制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和皮特·里彻森将这些社会限制称为“社会应急方案”:这套方案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禁忌和法律,这些禁忌和法律对冲动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我们通过婚姻、物权以及合同来鼓励长期投资和长期承诺。这套社会应急方案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通过惩罚短视行为和奖励富有耐心的长期行为,我们的社会因此可以采取更为先进成熟的生存战略(比如贸易、灌溉农业以及制造业),我们因此能够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取得更大的经营规模,实现更高的效率。这些更先进的生存策略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又有能力设计出更精细的冲动控制体系。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冲动和短视不断斗争的历史,我们的社会通过各种方法说服、强迫或其他方式引导个体压抑自己冲动和短视的倾向,只有当我们成功抑制这些不良习惯的时候,人类文明才可能向前发展。
然而,到了16世纪,我们发明了一些新的制度,包括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以及新教教义,随着这些制度的产生,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上述制度提高了商业自由度,保护了个人的政治权利,并让个人拥有直接与上帝交流的权利——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个人权力的放大。当然,这些制度的设计都十分精妙,把合作作为制度实行的前提,对个人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限制。比如,为了获得个人的民主自由,我们必须首先加入共同的公民义务网络,并同意为履行这些义务而节制个人的利益。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机会,我们承诺在进行贸易时秉承公平和诚实的原则;为了获得与上帝交流的权利,我们必须接受一种强调克制的宗教文化。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自由社会“通过剥夺个人的自然力量”来“赋予他们社会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使用”。在卢梭的理论中,社会与个人进行了这样的交易:给我耐心与合作,我将用集体的规模、杠杆、智慧来保证你获得长期稳定和安全的生活。只要接受这样的条件,你将获得靠个人单打独斗永远无法获得的幸福。
正是在这样的契约条件下,人类文明达到了辉煌的高峰(至少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如此),这种高峰可以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也可以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维多利亚时代所创造的空前财富和帝国雄风直接来源于一种极度保守的、高效的个人克制文化。同样,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一套新型的官僚主义秩序(包括政府、学校、公司以及其他科层组织,这些机构共同服从一种新的行为科学的指导)使用各种高压手段(从罪恶税和令人平静的建筑风格,到时间管理文化和步步为营的职业阶梯 [13] ),有系统地控制人类的冲动和短视倾向(同时控制很多其他方面)。
我们的社会从未停止过与冲动和短视的斗争,任何胜利都是暂时性的。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曾经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大部分人除了自我克制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匮乏和不安全的环境中,普通人的最佳生存策略就只能是向耐心与合作的社会规范投降。然而,一旦更高效的个人生存战略产生,一旦这种战略能够让每个个体更快、更独立地获得满足(随着19世纪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这种新的战略确实产生了),作为一个追求效率的物种,我们就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拥抱这种新的战略。我们很容易理解,当这种新的战略产生时,几万年来的社会控制开始失效,我们冲动和短视的本能即将再次获得释放。
时至今日,能阻止我们大脑边缘系统进行独裁的自然限制已经变得非常稀缺。虽然我们的收入增长缓慢,但数字化革命加速了效率的提升,能给我们带来基本满足的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食品变得极为廉价,以至卡通化的巨型包装成了很多餐馆爱用的营销策略:半加仑(约1.89升)的超大杯软饮料、深不见底的虾桶、无穷无尽的自助餐。(“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饮食哲学。)同时,无穷无尽的信息和娱乐便宜到几乎不要钱,于是人类仅存的怀疑精神成为我们自我克制的唯一来源。
习惯了物质稀缺的人类大脑必须适应物质过度丰富的现代社会,然而这还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在这个物质超级丰富的市场上,商家的营销策略尽一切可能利用我们的这一弱点,拼命挑动我们的冲动与短视。比如,大型制造商将青少年市场作为营销的重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家明白孩子和青少年由于思维发展上的缺陷,缺乏耐心和想象未来的能力,因此他们是最容易受市场宣传手段影响而过度消费的群体。再比如上文提到过的消费者信贷,虽然如今个人信贷变得极度廉价且容易获得,然而更危险的是,信贷产业的商家以上述神经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设计其市场营销策略(比如极低的“最低每月还款额”和超高的信贷额度),这些策略针对的正是我们思维上的漏洞和缺陷。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计算成本的降低,个人信贷的核心理念(将眼前的利益和未来的成本分离,将当下的快感和未来的痛苦分离)被植入消费者经济的所有方面。从快餐到娱乐,再到社会互动,几乎每一种消费体验都故意将即时奖励的成本推迟,在很多情况下,商家的设计是如此精妙,以至对消费者来说,好像眼前的享乐根本没有任何成本。如今获得满足的速度成了所有消费体验的首要评判标准。每季度,商家都会投入大量金钱和其他资源,只为将满足消费者的时间缩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亚马逊和eBay(易贝)等零售商正在尝试提供当日送达的快递服务。快餐店可以直接将外卖送到消费者的汽车里。 [14] (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用远程控制的机器人来完成这项任务了。)奈飞等在线影视公司能在一天内发布整季最新的电视节目,这样用户就可以马拉松式地(或者应该说“彻夜狂欢式”地)一口气看完一整季新剧。汽车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极度宽松的信贷标准,即使违约不付房贷的人也可以贷款购置最新款的皮卡。 [15] 有了智能手机上的各种App,你可以随时随地(在火车上、在朋友的公寓里,或者是面对杂志中的一幅图片)扫描商品的二维码,然后要求商家送货上门。 [16]
按照目前消费者科技的发展速度[可以实时传递商品的3D(三维)打印机、可穿戴的智能手机、逼真到可以提供性服务的机器人],未来人类的大脑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将望远镜拿反的习惯。市场与消费者自我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个关系的一端是不断赋予消费者更多能力的经济,而另一端是由于神经生理因素而必然滥用这些能力的消费者。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无法回头的毁灭悬崖。
当我们了解了人类思维方面的偏差,以及商家是怎样巧妙地利用(用现在的词汇说应该叫“挖掘”)这些思维偏差的,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要让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变得更加可持续是非常困难的,甚至降低这种消费主义经济的疯狂程度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如今,再想通过传统的压抑手段,通过自上而下的管制措施来控制个人的冲动只会导致惨败。比如,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曾试图禁止商家向消费者出售超大杯碳酸饮料的努力,以及任何试图改变枪械持有权的荒诞现状的努力。此外,通过复兴“耻辱文化”来鼓励人们自我克制的运动似乎也没有什么前途。比如,既不环保又不符合政治正确方向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屡禁不止。只有行为科学方面的进展让我们看到了微小的希望,某些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微妙调控手段也许能帮助我们克服人类大脑与生俱来的思维缺陷。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的研究者沃尔特·米舍尔发展了一套能够培养儿童耐心的有效训练策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因为缺乏耐心的儿童成长为缺乏耐心的成人的可能性极大。 [17] 此外,我们在行为科学的研究方面还取得了其他重要的成果,比如理查德·塞勒(双重自我模型的提出者)及其合作者卡斯·桑斯坦研究出的选择构建体系。选择构建体系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技术、基础设施及其他环境设计因素巧妙地引导我们采取更有耐心的行为,鼓励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能自动追踪我们每日支出的App,这些App在我们超支时向我们发送警告。
然而,在目前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上述努力就如逆水行舟一般艰难。我们的政治文化越来越鼓励个人对政策和政治事件做出快速、本能的反应。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市场一拍即合,两者共同排斥和拒绝任何影响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的因素,因为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最具正当性的个人目标(著名的雅皮士活动家杰瑞·鲁宾曾在1970年发出过这样的呐喊:“只要我们看到规则,我们就必须打破它。打破规则是我们发现自我的唯一手段。” [18] )。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未来越是充满不确定性,人类的短视倾向就会表现得愈加明显,而新的经济模式似乎正在让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最严重的短视偏差不是发生在消费者层面,而是发生在政府,特别是公司的制度层面。上文所提到的选择构建体系也许能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一些正面的限制,对制度上的问题却无能为力。在很多行业中,如今公司的高管拥有一整套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技术以及其他能力,因此他们可以实现非常快速的回报。对这些高管而言,他们不仅和普通人一样有对未来成本进行贴现的本能思维漏洞,而且他们所处的公司文化也充满了冲动和短视的哲学。在很多公司中,管理者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一旦任何机会出现,他们就必须尽一切可能抓住并挖掘这些机会的潜力。即使这些商业机会从长期来看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金钱的驱动和商业文化的压力仍会鼓励管理者追逐这些机会。比如,虽然大规模裁员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我们仍然经常看到公司管理者为了快速提升股价和保护个人的奖金收入而这样做。在金融行业中,这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日益成熟的技术让银行家和交易员有能力快速积累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同时将整个金融市场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在今天的金融板块中,从业人员不仅利用各种技术将风险和收益相分离,甚至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将风险重新转嫁(美其名曰“重新分配”)给其他人甚至整个社会。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的金融板块中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常规操作。上述现象可以部分归因于我们在跨期选择时的思维缺陷。但最大化个人收益和机构收益,却将未来成本转嫁给他人的倾向,事实上显示了我们思维决策方面的第二个漏洞,该漏洞不仅导致我们不能充分认识未来的后果,还导致我们缺乏重视未来后果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天普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基普尼斯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权力是否影响个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尤其是权力是否确实会导致腐败。在一系列实验中,基普尼斯设计了一种虚构的工作场景:一部分被试扮演经理的角色,另一部分则扮演员工的角色。在某些实验场景中,基普尼斯只赋予经理很少的权力:他要求经理通过劝说的方法要求员工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在另一种实验场景中,经理则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解雇员工、将员工转去其他部门,或者提升员工的职位。在实验过程中,基普尼斯观察了不同设定下经理的行为变化。事实证明,权力的效应是非常惊人的。基普尼斯发现,没有权力的经理通常会采用“理性的战术”,比如和员工商讨工作的目标;而拥有权力的经理则会尽量利用权力,他们更容易采取强迫性的“高压战略”,比如批评员工的表现,向员工提出要求,以及对员工表示愤怒。 [19] 拥有权力的经理更倾向于对员工的工作表示不满,他们也更容易将员工的成功归因于自己。此外,拥有权力的经理常常与员工保持心理上的距离。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基普尼斯提出了权力变质模型,他认为权力会导致自我意识的膨胀,并降低对无权者的同情心。 [20]
虽然基普尼斯的研究针对的是近40年前的职场环境,但他的研究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盛行的激进的自我营销文化。在基普尼斯的研究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证实了权力确实会改变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模式。超过10项研究显示,拥有某种权力(比如管理权限、社会地位或金钱)的个人更容易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违反社会规范。权力会让我们变得更粗鲁,更容易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更容易带着偏见看人,更倾向于作弊甚至违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保罗·皮福曾做过一项经典的心理学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皮福发现,社会地位高的司机(即驾驶豪车的司机)的驾驶行为更具有侵犯性:在一个不受交通管制的路口,高社会地位司机抢夺他人路权的概率是低社会地位司机的近4倍;当穿过人行横道时,高社会地位司机无视过马路的行人继续前进的概率是低社会地位司机的近3倍。
可能有人会说,不一定是权力导致了这些反社会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性格更积极、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比较容易获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力。但是,目前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显示,权力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哪怕我们只是暂时让被试认为自己拥有金钱和权力,也会促使他们产生更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更激进的行为。2012年,皮福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在实验中,两个被试会一起进行《大富翁》游戏,但是两人权力的分配却被故意设定得不对称。其中一位被试拥有更多现金,并且每次可以掷两个骰子;而第二个被试只有对方1/2的现金,每次只能掷一个骰子。从实验一开始,现金和骰子数量更多的被试(地位高的被试)就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行为。首先,地位高的被试占据了游戏桌更大的面积。其次,地位高的被试更不愿意与对手进行眼神接触,行为也更自由随意(比如帮地位低的被试移动棋子等)。在移动自己的棋子时,地位高的被试更加用力,移动棋子发出的声响可以达到地位低的被试的3倍(实验场地配备了分贝仪)。换句话说,地位高的被试虽然只是暂时被赋予了更高的权力,但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与现实社会中权力更大、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行为是一致的。皮福告诉我:“我们让被试参加一些不涉及重大利益的小游戏,在这些游戏中,我们故意将规则设定得不平等——这一点是完全透明的,地位高的被试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因为不平等的规则设计而暂时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然而在获得这些暂时的权力仅仅几分钟后,双方之间的权力角色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暂时获得微小权力的人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与我们在社会上见到的真正具有高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21]
为什么权力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呢?具体的机制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是研究者已经很好地理解了其中的基本原理。心理学家达谢·凯尔特纳是权力研究方面的先驱,他认为,关于权力和地位的感受启动了我们的“追求系统”,这一神经机制会促使我们更努力地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比如情爱、社会认同以及获得他人的关注;同时这种“追求系统”也会使我们更努力地去追求一些其他需求,比如金钱。凯尔特纳说:“一旦启动这种追求系统,它就会为你提供前进的动力,你会更热情地追求各种东西。”更重要的是,权力不仅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更激进,还会让我们对其他人的感受和社会规范变得更迟钝。凯尔特纳说,追求系统的启动和上述敏感度的降低能够产生显著的效应:“一旦你觉得自己拥有权力,任何东西看上去都不错,都非常值得追求。于是你会努力追求任何看起来不错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获得更大份额的公共产品,也可能是你的秘书,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22]
说实话,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并不需要什么理论支持,我们也知道社会上有钱和有权的人经常表现得像一群无耻的混蛋。但是,我之所以在此处列举各种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证据,是为了说明权力和唯我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强大和根本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冲动的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个人的实际权力正在下降,但我们却更激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提升,这已成为社会所有阶层的共同特点。目前的事实是,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战后时期我们曾经拥有的现实的、持久的、真正的个人权力(比如收入的提高、更受民意影响的政府机构、更有安全感的社区意识等)如今已变得非常缺乏。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鼓励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风潮今天却变得更为强烈,这种文化意味着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使用我们手中剩余的任何个人权力来进行激进的自我追求。同时,消费者市场不断发明各种新颖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让激进的自我追求过程变得更轻松、更高效,也更有可能发生。大量的商品和服务直接针对我们内心的渴求,公开鼓励消费者追求更激进的个人权力:商家设计出了超重低音的环绕立体声汽车音响,并在广告中公开宣传这种产品的目的就是让整个社区都对你羡慕不已;商家甚至还推出了简直能烧焦视网膜的高亮远光灯,这种远光灯的广告声称该产品能够彰显你“激进的驾驶风格”(即亮瞎对面司机的双眼)。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25年来汽车和卡车设计方面的变化趋势。在这方面,商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它们毫不含糊、毫无羞耻之心地把权力和对权力的滥用充分融入车辆的设计之中。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基思·布拉德舍的记者兼作家记录了这样的情况:底特律设计的汽车不仅比以前的车型体积更大,马力更强,甚至在外形方面故意设计得凶狠而令人害怕。比如,克莱斯勒的最新款公羊皮卡和杜兰多SUV在外观设计方面都故意模仿了食肉动物的外形。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再次推出了更大、更强、外形更吓人的新车型,更宽、更重的金属车身仿佛穿着厚厚的盔甲,车辆的高度也再次提升,让驾驶员能坐在指挥官一般的更高位置上。这些车辆不仅外形吓人,在交通安全方面也同样让人害怕。SUV司机的行车速度更快了,平均事故率更高了,同时由于车辆的体积、重量及其他配置的关系,他们在车祸中造成的损失也变得比以前更严重了。这方面的研究显示,虽然驾驶SUV可以显著降低司机本人在车祸中受伤的概率,但是被SUV撞到的司机受伤或死亡的概率却是被普通车辆撞到的2倍。 [23] 然而,这种安全方面的不平等居然成为SUV生产商宣传的卖点之一。一位与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商密切合作的市场营销专家克洛泰尔·拉帕耶曾明确表示,SUV车型这种几近野蛮的特点是汽车厂家故意为之,目的是刺激消费者的蜥蜴脑。蜥蜴脑是人类大脑中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经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促使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生存和繁殖的概率。人类的蜥蜴脑并不关心大型SUV所带来的所谓“外部成本”:高油耗、大量尾气排放,以及其他司机的安全。事实上,对蜥蜴脑而言,街上的每一个陌生人都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存,所有其他司机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与布拉德舍的对话中,拉帕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说:“我们的蜥蜴脑认为,如果出了车祸,我希望被撞死的是别人。”
SUV和蜥蜴脑的可怕例子充分展示了我们对个人权力的欲望是如何被商家利用的,这种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的社会环境。然而,消费者经济为我们提供的个人权力确实具有这样的负面效果,即使我们不用这种权力去伤害其他公民,至少可以利用这些权力避免与他人接触和交流。这种自由来自商家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便利:我们能够以越来越高的独立性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因此我们越来越少地依靠与他人的交流,也越来越无视他人的存在。比如,在食品方面我们就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创新:从电视餐到微波炉食品,再到不用下车就可以取餐的完全数字化的快餐售卖窗口,这些商业上的创新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味觉上的欲望,而不用再忍受烹饪或者与他人聚餐的“低效率”的行为。然而,这种个人权力的提升却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不仅烹饪艺术在不断消亡,而且全家坐在一起共进晚餐的社交习惯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这种个人权力对传统价值的侵蚀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种侵蚀正是消费者经济秘而不宣的目的之一。我们的消费者经济一直试图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大型零售超市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低的价格,还因为这种去个人化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将消费行为的社会义务降到了最低。20世纪70年代,沃尔玛首次向农村居民提供标准化的客户服务和海量商品(在同一家超市,你可以一次性找到从食品、服装、家庭用品、汽车用品、家用电器到药房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这种革命性的商业创新把我们从令人讨厌的低效率小镇生活中彻底解放了出来:我们再也不用拖着各种商品从一家小店走到另一家小店,再也不用忍受小型零售店要求我们履行的各种义务(因为商店店主同时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必须完成寒暄等社交义务)。也许,这种自由看上去不是革命性的,但杨百翰大学的社会学家拉尔夫·布朗曾说,这种自由标志着与传统的根本性决裂。布朗认为,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与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我们不可能仅仅扮演消费者这种单一角色。过去,买东西的人扮演的角色是顾客,这种角色带有各种社会条款和社会义务,要求我们在完成每一项交易前都要进行一些复杂的、耗时的社会互动。然而,现在零售商向顾客提供了单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机会,在这种效率更高的设定下,买东西的我们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而不再需要负担额外的社会义务,于是大多数人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新的角色。1989年,当沃尔玛刚刚进驻一家艾奥瓦州小镇时,当地的一位生意人曾向《纽约时报》抱怨道:“沃尔玛的进驻导致本镇的商业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24]
对很多保守派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从顾客到消费者的身份转换虽然看起来有些残酷,却是一种正面和必须的变化。这种变化让商家不得不适应效率市场的又一个基本的现实:消费者永远只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在陈旧的商业模式下,消费者可能不得不忍受消费过程中的社会义务(就像在股东革命发生之前,投资者不得不忍受商界的低效率一样)。然而在这种社会化的外衣之下,永远是对个人利益的冷酷无情的计算。1949年,保守派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泽斯曾这样警告过我们:“对消费者而言,除了他们自身的满足以外,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过去的美德或者既得利益。如果其他人能为他们提供更好或者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就会抛弃以前的供应商。在买家和消费者的世界里,只有冷酷无情的计算,没有对他人一丝一毫的体谅和怜惜。” [25] 对卖家而言,如果不能接受和适应上述事实,如果还想继续依靠社会义务及其他非市场化的低效率因素生存,那么不仅它们自身的经营注定会失败,还会降低市场的整体效率。效率市场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曾经断言,只有在每个人都尽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市场才能达到效率最高的均衡状态。因此,保守派的经济学家相信,从顾客到消费者的身份转化只是亚当·斯密伟大眼光的具体实现。也许这样的身份转化会伤害一些旧式的、低效率的商人,或者摧毁一些小型的乡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化可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然而,当我们以纯经济的达尔文式眼光来看待这种商业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时,我们其实忽视了很多重要的细节。亚当·斯密本人也曾经说过,只有很强的道德标准才能使市场达到著名的最优配置状态:如果买家和卖家之间失去了信任和同情,市场很快就会失去效率,甚至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数不尽的丑闻、欺诈以及泡沫的破灭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最佳论证。当经济中的买家从社会化的顾客变成完全经济化的消费者,必然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因此我们应该尽早对这样的现象进行干预,而不是等市场完全失灵时才追悔莫及。在这里我想再次举大型零售超市的例子。虽然它们以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商品为我们提供了高效的购物方式,但是它们同时也给这些获得个人权力的小镇消费者带来了一系列的成本。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乡村经济学家肯尼思·斯通的研究表明,在沃尔玛进驻一个新城镇后的两年内,距离沃尔玛距离不足20英里的所有本地商店都会面临销售量的下降,下降的幅度从1/4到2/3不等。这种巨大的损失导致小镇的很多中心商业区逐渐瓦解,不仅小镇的社区基础受到严重伤害,而且本地商店的倒闭还会减少当地居民的消费选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特洛伊·布兰查德的研究显示,在某些小型乡村地区,新进驻的大型零售超市的成功会显著增加居民购买食品的交通距离。此外,最近还有一些新的研究显示,本地商店的倒闭还会给乡镇带来一些额外的损失,因为相比于大型零售超市,本地的小型商店能为居民提供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沃尔玛的员工周转率高达每年50%),能更有力地支持本地的社会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其他保证社区生活质量的项目。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冲动的社会的核心矛盾: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个人权力,同时也摧毁了很多哺育我们的东西。
早在1953年,离我们开始对个人权力危机进行数量化的度量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自由派学者罗伯特·尼斯比特就已经对个人权力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警告。尼斯比特在其经典著作《社区的探索》中警告我们说:虽然现代的自由社会把个人从压抑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解放了出来,但这种社会变化也同时将个人从“习惯、传统以及社会关系的微妙而无尽的复杂综合体”中孤立了出来,这种复杂的综合体正是个人自由存在的先决条件。人类生来就是社会动物,因此个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结构(如家庭、教堂、社区、邻里或志愿者机构等)的支持下才是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尼斯比特认为,随着现代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上述社会结构显著退化甚至逐渐被抛弃,于是“每个人几乎都变成了完全孤立的单个原子”,社会中的人变成了单独的个体,人们感到“被孤立并失去了归属感”。 [26]
尼斯比特的学说是自由主义思想阵营发出的最清晰的呼声之一。尼斯比特认为,这种孤立趋势的最大推动者是自由国家及其强大的穿透作用,这种穿透作用通过官僚系统、津贴补助以及专家权威的渠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同时,尼斯比特也非常担心商业市场对社会纽带的侵蚀作用,他认为“高度理性化和去人格化的经济世界”会削弱家庭、村庄以及其他“中介制度”的功能,使得这些制度无法继续发挥“安全与忠诚中心”的作用。随着亨利·福特生产的汽车进入美国的农村家庭,原先维系这些家庭的社会纽带开始逐渐减弱或消失,一个世纪以后,所有社会依存关系完全解体为一种工业化的目标。年复一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将社会义务、规范以及其他所谓“低效率”的元素从消费行为本身剥离,我们的目标是将消费纯化至其最本质的功能:一种为自我而存在,以自我为单位进行,完全关乎自我的个人行为。更重要的是,随着不受任何限制的消费行为逐渐变成商业经济的主流模式,并且成为生产者利润的最重要来源,这种完全不受限制的消费模式已越来越多地被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认同和庆祝。我们先是迎来了“自我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标志是对个人实现的强烈追求和对传统的反叛。接着,大约10年之后,出现了以效率市场理论为核心的经济个人主义风潮。不管意识形态方面的潮流如何变化,这些文化现象向我们传递的深层次信息都是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明示或暗示鼓励我们勇敢地追求个人利益。我们的文化不仅认为个人利益可以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分离,甚至鼓励我们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
在这样的文化风潮下,新一代公民认为他们的自我是高于一切的存在,这种信念有时表现为一种隐含的态度,有时则赤裸裸地直抒胸臆,而从顾客到消费者的身份转化只是这种文化倾向的一个标志而已。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向上攀爬,日益接近最完美的消费高峰时,我们却发现脚下的大地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我们将消费行为完全私人化的同时也摧毁了现代社会仅存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正是控制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蜥蜴脑)的最后一道防线。比如,家庭烹饪曾经合理地限制了我们对热量的摄入,如今随着快餐和方便食品的流行,这种限制已逐渐消失殆尽。对怀孕的恐惧曾经起到过限制婚前性行为的作用,而避孕药的发明使这种限制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格概念也被弱化了,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要达到完善的人格,一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共同价值的纪律”,如今这种价值观几乎已经消亡。我们不再谈论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而是鼓励每个人追求所谓的“个性”。如今,自我提高意味着“不断寻找个体与他人的差异”,而实现自我提高的途径往往是不断消费。 [27] 我们常常听到保守派人士对如今的个性化价值观进行强烈的抨击和反对,虽然他们支持的旧式价值观常常是压抑性的、不公平的、歧视性的,甚至带有中世纪的刻板元素,但这些古老的道德标准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控制我们的冲动。如今,这些旧式价值观因被视作高效消费行为的障碍而被完全摧毁。也许,更合理的做法是用一种不那么古板的新式社会准则取代这些古老的价值观,但由于旧道德被迅速摧毁,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旧道德被不由分说地连根拔起,事先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认真的考虑,也没有人认真权衡过这种变化的成本与收益。摧毁旧道德的过程完全是自动的、不加思索的,因为自由市场向我们提供了更多、更高效、更能让商家获利的自我表达的权力。
简单来说,今天的消费者虽然拥有了更多的个人权力,却也在享受这些个人权力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孤立。在进行消费狂欢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古老价值观的指引,这种矛盾的处境让我们中的很多人深感不安。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经常向我们描绘一种全能的、胜利的消费者形象,我们的内心却并不总是这样欢愉。焦虑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多心理健康专家认为社会纽带的弱化是诱因之一。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这样写道:“从前,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还有家庭、教堂、朋友等种种社会资本作为缓冲,如今这些社会纽带已变得越来越脆弱,它们不再能抚慰个人的失败与痛苦。在过去的25年中,摆脱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的种种束缚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然而,在今天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我们却不得不为这一趋势付出沉重的代价。” [28]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普特南等学者认为,解决之道是复兴日益衰落的社区联系。然而,另一种解决方案却让我们深感不安,很多消费者希望能从别的途径获得支持和引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求助之手伸向为我们提供新权力的商业生产者。于是,我们让食品生产公司决定晚餐的最佳分量(现在的分量比40年前大出许多),我们让汽车生产商决定车辆的最佳马力和速度。
同样,我们也让银行决定我们究竟应该借多少钱。上文提到的行为学家迪利普·索曼的研究显示,很多人在决定信用卡支出的时候不是取决于自己的需求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银行向我们提供多少信贷额度。也许在信贷紧张的时代,这样的行为曾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放款人在发放贷款之前通常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进行详细的审核,以确保我们有能力偿还债务。随着追求大量贷款和快速回报的银行业模式的兴起,上述逻辑已不再成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些银行机构专门以信用极差的消费者为放贷目标,因为这些人通常无法及时支付信用卡欠款,是银行不断收取滞纳金的最佳对象。除此之外,金融机构针对我们的每一种思维漏洞设计出了花样繁多的营销策略。比如,大幅提升信用额度,减少每月最低还款额,因为这样做能让消费者产生自己拥有更多财富的幻觉。如今,对金融机构而言,消费者的思维漏洞变成了重要的利润来源。1989年,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曾发表过一份措辞严厉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沃伦指出:“一些借款人的短期债务数额巨大,连支付利息都有困难,更不要提支付本金了。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仍然愿意向这类借款人发放第4张、第6张,甚至第7张银行卡,并批准他们用信用卡消费。”
到了世纪之交,美国的消费者即将踏入一场完美的风暴。许多人拥有的个人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负担和合理管理的程度,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过度的个人权力导致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混乱,也使这些权力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失去了传统价值观的引导,我们越来越依赖市场本身,靠市场来告诉我们究竟应该使用多少个人权力。到了21世纪初,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将美国经济推上了过热的道路。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迫近,还准备继续推出一轮又一轮新的消费“工具”。很快,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种畸形的文化最终会导致灾难降临。
[1] Interview with author.
[2] Michelle J. White, “Bankruptcy Reform and Credit Card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 pectives 21, no. 4 (Fall 2007): 175–99, http://www.econ.ucsd.edu/~miwhite/JEPIII.pdf.
[3] Reuven Glick and Kevin J. Lansing, U.S. Household Deleveraging and Future Consump tion Grow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Letter, May 15, 2009,http://www.frbsf.org/publications/economics/letter/2009/el2009-16.html; and “U.S., World’s Growing Household Debt,” research paper, June/July 2004, http://www.marubeni.com/dbps_data/_material_/maruco_en/data/research/pdf/0407.pdf.
[4] White, “Bankruptcy Reform and Credit Cards.”
[5] Richard H. Thaler, Quasi Rational Economics , p. 78.
[6]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Adam Smith, Behavioral Economist”,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www.cmu.edu/dietrich/sds/docs/loewenstein/AdamSmith.pdf.
[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8] Ibid..
[9] Michael E. Lara, “The New Science of Emotion: From Neurotransmitters to Neural Networks,” SlideShare, http://www.slideshare.net/mlaramd/science-of-emotion-from neurotransmitters-to-social-networks.
[10] 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和神经动力学专家乔纳森·海德特曾这样写道:“当你想到自己讨厌的政客,或者和自己的配偶发生争执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过程。你就好像马上要上法庭做证一样,开始准备你的辩护词。你的逻辑推理能力不由自主地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论点。这些论点都支持你的意见,而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反对和攻击。”参见Haidt,“Moral Psychology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Edge.org,Sept. 21,2007。
[11] George Loewenstein, “Insuff icient Emotion: Soul-Searching by a Former Indicter of Strong Emotions,”Emotion Review 2, no. 3 (July 2010): 234–39.
[12] 而大脑边缘系统非常讨厌用现金购物,因为现金被视作一种需要保护的财产,一旦我们花费了现金,大脑边缘系统就会将其视作一种损失。于是大脑边缘系统会在我们的大脑中释放出大量导致反感情绪的神经递质,从而抵制这种消费行为。
[13]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
[14] Vivian Yee, “In Age of Anywhere Delivery, the Food Meets You for Lunch,”New York Times , Oct. 5,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06/nyregion/in-age-of-anywhere delivery-the-food-meets-you-for-lunch.html?hp.
[15] 事实上,只要你还没有破产,你就会收到各种金融中介和信用卡公司的广告,邀请你通过借钱来“重新建立个人信用”!
[16] Hilary Stout, “For Shoppers, Next Level of Instant Gratif ication,”New York Times ,Oct. 8,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08/technology/for-shoppers-next-level-of instant-gratif ication.html?hpw.
[17] Jonah Lehrer, “DON’T! The Secret of Self-Control,”The New Yorker , May 18,2009,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5/18/090518fa_fact_lehrer?cur rentPage=all.
[18] Cited in Thomas Frank, Commodify Your Dissent , p.32.
[19] Leonard N. Fleming, “David Kipnis, 74, Psychology Professor,” obituary, Philly.com,http://articles.philly.com/1999-08-29/news/25482558_1_psychology-professor-social psychology-absolute-power; Kipnis quoted in David M. Messick and Roger M. Kramer,eds.,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hip: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20] Fleming, “David Kipnis, 74.”
[21] Interview with author.
[22] Interview with author..
[23] Jeremy Laurance, “4x4 Debate: Enemy of the People,”The Independent , June 23,2006,http://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health-and-families/health-news/4x4-debate-enemy-of-the-people-405113.html.
[24] Jon Bowermaster, “When Wal-Mart Comes to Town,” April 2, 1989, http:// www.nytimes.com/1989/04/02/magazine/when-wal-mart-comes-to-town.html?pagewanted=all&src=pm.
[25] “The Sovereignty of the Consumer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http:// mises.org/humanaction/chap15sec4.asp.
[26] “Robert Nisbet and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http://mises.org/media/4211.
[27]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 pp. xxiv.
[28] R.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J. Simon & Schuster, 2000) p. 335.
2005年夏天,当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房地产市场就像一台巨大的印钞机一样不断创造着财富。星期日午后的最佳的去处是拉斯韦加斯硬石咖啡馆的舞池。硬石咖啡馆每周都会举行所谓“康复派对”,派对现场充满了DJ(唱片骑师)的音乐、酒精以及大量小麦色的皮肤。从中午开始,硬石咖啡馆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派对的大部分是来赌场消遣的游客,但也有一些本地人。本地人中有不少来自拉斯韦加斯的房地产业,他们在音乐声中一边用酒精制造宿醉,一边兴奋地唠叨关于房地产市场疯狂升温的暴富故事。当时,拉斯韦加斯的房地产价格每年上涨50% ,凡是有能力参加这场财富狂欢的人都挤进房地产市场来分一杯羹。有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镇以外的沙漠地带建起大片大片的住宅区。来自中国香港和韩国首尔的精明投资者眼疾手快地购入各种价格飞涨的奢华高层住宅,来自加州橙县的医生和牙医们像短线交易者一样频繁买卖着拉斯韦加斯的房产。
除了这些专业的投资人以外,还有另一种业余的投资人。马古先生就是这样的业余投资者,他进入房地产市场完全是偶然。马古先生是拉斯韦加斯本地人,最初他发现自己家的房子价格翻了一番,于是他利用这笔飞来的横财加入了炒房的热潮。像马古先生这样的业余投资者通常先通过对自己的房屋进行再次融资获得一笔现金,然后用这笔现金购买第二套房产,几个月后再将房产卖出,获利三四万美元。那时,赚钱是如此容易,一位当时在拉斯韦加斯工作的房贷放款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啊,我这么轻松就让自己手里的钱翻了一番,我肯定是个天才!于是他们又去买第二套、第三套,甚至更多的房子,然后再转手卖掉。接下来这些人就会想:我的银行账户里现在有10万美元了,那我为什么不继续‘炒房’呢?” [1] 到了2005年,一些像马古先生这样的投资者已经拥有了5处、6处,甚至20处房产。他们的做法导致拉斯韦加斯大约有一半的房屋销售来自以‘炒房’为目的业余投资者,这意味着拉斯韦加斯地区的很大一部分新房产掌握在一些根本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手中。一位资深房地产从业者托德·米勒告诉我:“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投资者,真正的投资者通常会买入1处房产,然后在持有该房产期间通过出租获得现金流。另外一些真正的投资者会在市场上寻找价格被低估的房产,并精确计算修理和翻新这些房产所需的费用。而这些业余投资者根本不会这么做。他们‘炒房’的行为和在赌场上掷骰子没有什么不同。” [2]
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马古先生这样的业余投资者。在美国,房地产业的监管十分宽松,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房产经纪人。更重要的是,业余投资者的狂热导致整个信贷系统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做出了种种改变。在21世纪初,几乎每个人每天只要打开邮箱或电视机就会收到一些金融公司发来的再融资邀请。银行不仅扩大了抵押贷款业务的规模,还将整个贷款过程完全自动化。高效的自动化贷款流程使消费者取得抵押贷款就像申请信用卡一样容易。一位曾在拉斯韦加斯工作的信贷业务员这样告诉我:“想借钱的人只需要告诉我们其年收入和资产情况就行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提供任何证明,也不看他的银行流水单。你甚至还可以申请一种名为‘NINA’(无收入无资产)的贷款,这种贷款不要求借款人有任何收入和资产,只要填写你的姓名、地址以及社会保障号码,就能获得贷款。我们甚至从不打电话给借款人的雇主核实情况,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借款人的雇主是谁。在我们的申请表上没有雇主电话这一栏。你可以申请高达抵押物价格100%的贷款。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情况,确实太疯狂了。” [3]
确实,如果想看看冲动的社会的最高峰到底能达到何种疯狂的高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是我们的最佳研究对象。只要我们去过房地产高峰时期的拉斯韦加斯、橙县、迈阿密、菲尼克斯(或者马德里和都柏林 [4] ),或者当时全球上百个房地产热点城市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很难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的胜利抱有任何怀疑态度了。在这些地方,在房价飞涨的热潮中,过去50年来的所有冲动与混乱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技术以及神经化学的有毒混合物。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对自我表达的疯狂推崇和对人类思维弱点的疯狂利用;看到人们为恢复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生活水平而狂热挣扎;看到人们盲目地拥抱效率市场理论,非理性地接受任何效率市场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个人权力,不管这样的权力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多么不负责任、多么缺乏说服力。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在金融泡沫的最前线,我们看到自我与市场、心理学与经济学是如何以最自然的姿态、最高的效率互相成全着对方的。因为从很多角度看,金融板块是整个市场中最受心理因素影响的部分,金融板块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自我。金融板块就仿佛整个经济体的蜥蜴脑部分,它扮演的是短视的冲动者这一角色:一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出高度创新、资源丰富、不知疲倦和高效率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的、完全不知羞耻的。这样一位短视的冲动者会毫不犹豫地将理性计划者和社会的其他部分推下财政的悬崖。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曾封锁、压抑我们的金融板块,用各种法规和监管标准抑制其活力(事实上人类也曾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自我克制)。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们以前的这种做法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充分释放金融自我很容易导致灾难,过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曾经对开放金融板块的危险心存恐惧。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像我们冲破了很多其他限制一样,我们征服了对金融灾难的恐惧。我们掌握了新的技术和理论,并相信这些工具能帮助我们驯服金融板块的能量,让金融板块在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基于同样的乐观心态,我们也曾相信我们用消费者经济的工具完全驯服了自我。于是,我们开始尝试放松对金融板块的控制,并将财富增加的希望寄托于金融板块——事实证明,金融板块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通过信贷发放,金融板块使消费者可以借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于是经济扩张的速度超越了物质和时间的限制。然而,在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中,金融板块也逐渐淹没和控制了我们。被释放的自我重塑了我们的消费者文化,让整个消费者文化不断适应我们永远无法满足的标准;同样,金融板块重塑了我们的整体经济(同时也重塑了大部分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文化),以不断满足其蜥蜴脑式的冲动欲望。到21世纪初,随着马古先生这样的投资者在房地产市场上大展身手,我们的金融系统将整个经济改造成了最符合我们自我需要的样子:极端冲动,完全投身于对短期满足的追求,完全不考虑后果。
应该指出,我们的金融板块并不总是这样冲动和鲁莽。在1929年的股灾发生以后,金融板块被勒令闭门思过,在收紧管制以后,整个金融产业重新调整了自身的定位,开始发挥辅助实体经济的作用。当时的银行业人士和其他金融活动参与者采取保守的低风险投资策略,“资本应保持充分的耐心”成为一句著名的格言。在这种保守的策略之下,金融业取得了中速的、稳健的回报:在整个战后时期,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以及房地产业)的利润只占所有公司利润的不到10%。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在各个方面,混乱全面淹没了秩序,金融业的耐心和稳健姿态也被一扫而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来自外国银行的竞争很快吞噬了传统投资项目的利润,于是银行家、投资者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策略,以追求更高、更快的回报。几乎在一夜之间,“资本应保持充分的耐心”的投资哲学迅速被追求高收益率的疯狂所取代。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投资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任何能提供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负债收购、贵金属、食品类大宗商品、原油期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债券。
然而,最容易获得收益的“猎场”还要数北美和西欧的消费者经济。在这些地方,金融板块逐渐进入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金融板块达到了空前的规模:21世纪初,美国金融板块的利润已经占到所有公司利润的近25%。随着规模和所涉及范围的扩大,金融板块的影响力也大幅上升。我们越是依赖金融板块,就越容易受到其冲动个性的影响,去追求更快的、更高的回报率。在消费者信贷领域,显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信贷市场所倡导的即时满足和延迟成本的哲学很快也变成了消费者自身的哲学。但是,这还远远不是问题最严重的方面。经济的其他领域也普遍感受到了这种“金融化”所产生的深层次效应。比如,政府开始不断提高国家的负债水平——自由市场保守经济学的支持者罗纳德·里根总统最先发现,靠借款来融资政府预算,比保持预算平衡容易许多。决策者们越来越屈服于民众的欲望,也越来越依赖债务市场。当克林顿总统试图开展一场改善基础设施和学校建设的政治运动时,很多债券交易者开始担心大幅增加的政府开支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加剧,于是他们大量购入债券,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 [5] 此举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威胁到了克林顿总统连任的机会(据报道,克林顿曾抱怨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连任的机会取决于一帮混蛋债券交易员?” [6] )。不难看出,美国政府也同样受到金融市场短视性格的影响。
然而,受金融市场的短视性格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的公司经营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的股东革命以来,不仅美国的CEO越来越急于取悦金融市场(因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平均有2/3是以公司股票和期权的形式发放的),而且金融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取悦。 [7] 今天的股票市场是由所谓的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其中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尤其巨大,他们常常大量购入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后试图影响公司的股价。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总共控制了大型公开交易公司约3/4的股票份额,对这些大型机构投资者而言,对高收益的追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目标。 [8] 为了生存和繁荣,大型机构投资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取悦自己的顾客,它们的顾客范围很广,从退休老人到亿万富翁都在此列。为了取悦客户,大型机构投资者会为其投资组合设定相当激进的季度投资回报率目标。经济学家埃里克·蒂莫格尼和兰德尔·雷曾经指出,机构投资者设定的这些回报率目标通常都远远高于美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为了达到这样的高收益率,基金经理必须不断地“变换”它们的投资组合,买入表现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公司股票,同时卖出表现不佳的股票。因为机构投资者占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它们这种不断买进和卖出的行为会打破股价的平衡,产生对市场的扰动。换句话说,基金经理的买卖行为很大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交易行为做出反应,这种反馈机制的循环会不断提高基金买卖股票的频率。事实上,对投资组合的“变换”成了金融市场的新常态。在20世纪70年代,机构投资者买入股票之后平均会持有这些股票7年时间,然后再卖出,而今天基金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只有不到1年。 [9] 今天金融市场上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具备了恋爱指南中警告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情人的所有特点:冲动、短视,不愿意做出长期承诺。
对上市公司而言,金融市场上股票周转率提高的现象让它们很难适应。因为如今股票市场的大部分重要投资人对公司股价的细微波动都很敏感,并且这些大型机构投资人可以随时大量抛售手中的股票以表达对公司业绩的不满,从而大幅压低公司的股价,于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管理影响股价的因素上。然而,实际上,很多影响股价的因素并不能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一定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由于公司的季度利润报表会严重影响公司的股价,管理层不得不尽一切可能保证下季度公司的利润达到预期标准,有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损害公司未来的利润。在一份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这份调查问卷的对象是400多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当被问及是否会为实现本季度的利润目标而推迟对一些能产生丰厚利润的长期项目的投资时,有1/2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此外,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证本季度利润达到预期目标,他们愿意削减研发、维修、广告以及人才招聘方面的投资,而上述方面的投资显然是公司长期利润的重要保证。同样,为了保护当季度的利润数据,很多公司都倾向于尽快兑现任何形式的收益,虽然这很可能导致公司错过未来很多可以获利的机会。在另一份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向一些英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项目一可以在明天为公司创造250 000英镑的利润,而项目二能在3年之后为公司创造450 000英镑的利润,那么究竟哪一个项目更值得投资?大多数受访者都选择了项目一。 [10] 不难看出,大部分公司管理人员都犯了跨期选择方面的错误。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过,在行为经济学家对消费者的研究中,这样的错误也曾经一再出现。然而,在公司层面,这种错误的跨期选择却变成了标准化的经营模式。经济学家希瓦·罗基戈帕写道:“在如今的公司文化中,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已经变成了一种‘愚蠢的行为’。”罗基戈帕是公司财会方面的专家,也是上文提到的2005年调查问卷的作者之一。罗基戈帕说:“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家伙没有任何的长远眼光。他们最多着眼于未来的2~3个季度的情况。” [11] 由于事实上商业公司之间需要为争夺投资者的注意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任何能够快速提高公司利润和股价的经营策略都会很快被其他公司效仿。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司战略专家格雷格·波利斯基和安德鲁·伦德这样描述:“一旦一家公司为了提高当前的利润而牺牲公司的未来,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就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来保证自己公司的股价不会被比下去。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大家的事业前景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12]
显然,所谓的效率市场并不应该以这样的形式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说,效率市场应该鼓励公司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公司的股价反映的应该是公司的长期经营状况和利润水平。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公司股价应该等于公司所有未来利润的净贴现值总和——把未来公司挣到的每一分钱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换算为今天的贴现值,然后进行加总求和。因此,任何威胁公司未来利润的因素(比如管理层没有在长期研发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都应该引起投资者的担忧和不满。这样的担忧和不满本该导致很多投资者抛售该公司的股票,从而压低公司的股价,对管理者的短视进行惩罚。用罗基戈帕的话说,在真正理想化的效率市场中,如果公司的管理人员“采取伤害公司价值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市场发现,管理者未来的薪酬也会因此而降低”。 [13] 然而,在现代的公司财务中,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斯彭研究所专门研究公司短视问题的专家朱迪·萨缪尔森对我说:“如今的股票市场完全着眼于公司的短期表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很多成功的大公司(这些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支柱,而且历来是各种前沿科技的创造者)在进行长期投资时都只能采取特别小心翼翼的态度。”在研究中,萨缪尔森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2011年谷歌公司宣布增雇1 900名员工时,谷歌的股价立刻大幅下跌,最终跌幅超过了20%。 [14] 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投资者不喜欢公司做出任何增加支出的决策,即使这些支出有时是为公司的长期表现进行有价值的投资。 [15]
市场对长期投资的反感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根据航空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CEO诺曼·奥古斯丁的回忆,20世纪90年代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层人员曾经与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们会晤,向他们展示公司即将投资的尖端科技项目。然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演示会还没有结束,这些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居然“迫不及待地跑出会场,去抛售我们公司的股票”。在接下来的4天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1%。这让奥古斯丁极度震惊,因此他致电其中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股票分析师。奥古斯丁问他,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投资新的科技项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市场要对这种完全正常的经营行为进行惩罚?根据奥古斯丁的回忆,当时他的分析师朋友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第一,你们的这些研究项目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更何况没人能保证一定会收回成本。第二,你们的股东平均持有公司股票的时间只有18个月。15年以后,你们的股东很可能已经转而持有波音公司的股票了,因此股东并不希望你们想出好点子。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股东并不想要为你们的好点子付钱。’然而,这还不是最令我痛苦的评论。接下来,我的这位分析师朋友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他说:‘你们的管理层太短视了,我们才不愿意投资这样的公司呢。’是的,你没有听错,这就是那位分析师的原话!” [16]
当然,大型上市公司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止支出。然而,这些钱越来越多地花在追求能在短期内提高股价的方面。以股票回购策略为例,20世纪80年代,很多公司发现,提升公司股价最快速的方法(除了宣布大规模裁员以外),就是用公司的利润从公开市场上大量回购本公司的股票。此举将这些股票从公开市场上移除,于是这些股票便停止了流通,公司普通股票的供给量受到了限制,股价也就因此上升了。公司管理人员很快发现,通过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不仅可以迅速抬升公司股价,而且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薪酬。最棒的是,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投资新的经营活动(比如建立新的工厂、开发新的产品或雇更多的员工)却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风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回购本公司股票被视作操纵市场的非法行为。然而到了1982年,里根政府却承认了股票回购策略的合法性,并将其视作自由市场革命的重要部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票确实具有合理性(比如公司想要击退恶意收购者的进攻),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公司采用股票回购策略并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其目的仅仅是人为抬高股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每年花费2 0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占公司总利润的1/4。 [17] 显然股票回购策略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合理的理由,抬升股价早已成为唯一的理由。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实际产出(比如汽车、棉花、煤炭)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股价。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的产出不再是汽车、棉花、煤矿,而是股价。至此,我们完成了工业效率革命的最后一步:资本效率的革命。整个商业世界的目标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资本直接转化成股东的价值和管理者的薪酬。
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财富的甜蜜,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苦果。在过去的20年中,股价飞涨为大大小小的美国投资者带来了巨额财富,尤其是少数公司高管因此成了亿万富翁。然而这种财富的繁荣却掩饰甚至催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深层次问题。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很多公司为了追求高股价开始故意夸大季度利润数字。1992—2005年,对过去的报表进行利润“重报”(这种做法实质上等于承认过去财报上的利润数字被夸大了)的公司从每年6家 [18] 上升到了每月近100家。 [19] 各种各样的利润诈骗丑闻层出不穷:世通公司通过采用“创新性”的财会手段,将公司利润夸大了90亿美元;而安然公司则通过特殊目的机构隐藏了公司230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丑闻仅仅是问题的开始而已。真正的灾难是华尔街对资本效率(即不择手段追求资本的高回报率)的狂热追求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消费者心理的领域。
到了2002年春天,拉斯韦加斯的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开始觉得房地产市场有些不对劲了。在售房现场的展示会上,很多买家拿出的是一种很不寻常的银行贷款手续:这些银行贷款的利率很高,而首付却低得惊人,甚至出现了零首付的贷款形式。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收入和资产非常丰厚的借款人才可能获得零首付的贷款。然而当时的银行业却开始向首次购房的消费者提供这种贷款,其中有些人根本不具备购买房产的经济能力。当时在拉斯韦加斯从事房地产经纪工作的亚当·芬恩告诉我:“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零首付贷款了。于是我们这些业内人士不禁开始纳闷:这些金融机构究竟在干什么?” [20]
我们的金融机构究竟在干什么呢?原来,高盛、美林证券以及其他大型投行发现了一个追求高收益率的新领域:那就是被蜥蜴脑的狂热冲动所控制的房地产市场。 [21] 21世纪初,投行开始收购金额巨大的住房抵押贷款,然后将这些贷款组合起来变成一种证券,名为CDO(担保债务凭证)。投行将这种CDO转而出售给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市场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十分强劲:因为根据投行的宣传,CDO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抵押贷款借款人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款项),但只需承担很低的风险(因为这些贷款有房产作为抵押)。从资本效率的角度来说,CDO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投资方式,因为它可以把长期的实物资产转化为短期的快速回报。
这种新型的高效投资工具一面世就供不应求。事实上,由于对CDO的需求过于强烈,投行已经没有足够的抵押贷款来支持它们产出新的证券了。因此,投行开始鼓励和刺激消费者申请更多的抵押贷款。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并不是说突然之间有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收入增长的停滞,也许事实上能买得起房的人变得更少了),于是对投行来说,要想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贷款的标准。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华尔街开始对放贷机构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鼓励它们降低信贷标准。当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显然不合理的要求。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从事信贷发放工作的比尔·达拉斯曾就美林证券的情况接受《名利场》杂志的采访,美林证券是当时最大的抵押贷款证券发行人。在这篇访谈中,比尔·达拉斯说:“他们从未明确要求我们发放低质量的贷款。但他们会对我们说:‘你得增加优惠券呀。’”所谓“优惠券”指的正是高收益率的CDO。然而根据达拉斯的说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发放低质量的贷款。” [22]
虽然一些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资深人士对信贷标准的无限放宽表示了担忧,然而他们的忧虑根本无法战胜宽松信贷标准带来的淘金狂潮。与房地产有一点关系的人都开始赚钱,有人甚至在短期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仅佣金一项就为华尔街的银行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开始采取能降低成本(然而常常牺牲建筑质量)的高速建筑方法,瞬间建起数万间房屋,收获巨额利润。奋战在房地产热潮前线的人们简直就像泡在现金中一样。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拉斯韦加斯,忙碌的房产经纪人一年可以收入50万美元。而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的年收入甚至达到了100万美元。一位当时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过去我每年收入5万美元,而那时我一个月就可以赚5万美元。我们每晚都出去狂欢。我们去脱衣舞俱乐部,去参加各种狂欢派对。有时候你早上醒来,会看到一位色情片明星正在你的厨房里走来走去。然后你起床赶到办公室,继续度过疯狂的一天。”那些疯狂的日子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里的钱来得太容易,这里的姑娘都是免费的。”
房地产热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你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就可以通过“炒房”赚钱。只要拥有一套房屋,你就可以加入“炒房”的队伍,什么也不付出就能赚到大把的钞票。在拉斯韦加斯这样的房地产热点城市,房屋的价格几乎可以翻上一番,贷款机构开始遇到一些“连环再融资”的投资者,这些人每过6个月就会对手头的房屋进行贷款再融资,每再融资一次可以获得4万~5万美元现金。这些现金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被用来度假、购买食品,或者支付房贷。实际上,这些连环再融资的投资者利用了金融技术上的漏洞,把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卖给自己。这种行为就像是埃舍尔的绘画作品,就像一台违反了物理定律的永动机。这种行为违反了供给与需求的基本经济原理,也违反了劳动和所得的基本规律,然而这些奇怪的现象却在大环境的纵容下一再发生。一位银行从业者告诉我:“这种情况意味着,你可以从事公司前台之类的低收入工作,却拥有令人惊叹的豪华生活方式。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再工作谋生,不断对自己的房屋进行再融资就是你的工作。”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拉斯韦加斯。连环再融资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形式,同时也成了消费者经济和自我身份维持的新引擎。2003—2005年,美国人从自己的房屋上获得了近1.3万亿美元的资金,这笔巨款的1/3被用于购买车辆、游艇、等离子电视机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消费品。 [23]
连政府的决策者也被这种病毒所感染。在美联储,另一位自由效率市场理论的支持者——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快速攀升的房地产价格以及公众从房地产中获得的资金可以帮助政府解决消费者收入增长迟缓的问题。在这种过分乐观的形势下,美联储决定长期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通过这样的政策,政府希望金融市场能够完成传统经济活动不再胜任的任务:保持美国公众的生活水平继续稳步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同样犯了短视的毛病。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曾说:“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比率的上升不仅没有损害房屋拥有者的利益,反而改善了普通房屋拥有者的金融状况……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对总体经济情况起正面支持作用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在距离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办公室不足45分钟车程的城郊地区,新的房屋建设项目还没有开工就已经全部售完;在房屋完工之前,很多公寓就已经被转卖了两次甚至三次。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在金融板块提供的强大动力下,又一次焕发了新的活力。免费的午餐在当时竟成了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
如今,回顾当时的情况,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随着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结束和股东革命的兴起,美国的个人收入停止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事实上,上述金融业的不正常情况试图以不合理的方式来填补消费者收入方面的缺口。因此,这样的繁荣注定是虚假和暂时的。然而,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说不。整个金融板块都忙着大桶大桶地掘金。决策者们忙于庆祝他们“拯救”美国经济的英勇成就。显然,消费者完全无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管理。不仅消费者的蜥蜴脑被完全调到了狂欢模式,传统的社会制度(比如不愿借贷的传统价值观以及紧密的社区联系)也早已被以自我为中心的效率经济严重削弱了。这种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缺乏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地方(比如拉斯韦加斯)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不断用手中的房地产套取现金的投资者处于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我们熟悉的、能够限制个人狂热情绪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煽动狂热情绪的各种刺激和诱惑因素。拉斯韦加斯的一位资深信贷咨询员米歇尔·约翰逊这样对我说:“很多新到拉斯韦加斯的‘炒房’者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他们并没有和(大家庭的)家人一起前来,也不认识周围的邻居。因此他们没有很强的社区意识,也缺乏周围人的监督和规劝。没有人会对他们说:‘嗨,别傻了,这样不行。’” [24]
早在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在描述人类感情发展过程的时候,就发明了一个术语——“现实原则”。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健康的个人由于受到现实原则的限制,必须学会如何延迟满足。如果不能学会向现实妥协,继续坚持快感原则,那么这个人就会永远停留在感情功能不完善的幼儿期,既不能完成自我实现,也无法进行社会交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实原则主要通过社会结构的渠道对个人产生影响和限制,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家庭和制度的权威。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完全可以推广到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上。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如果个人或机构无法学会延迟经济满足,他们很快就会被效率市场排斥。
然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现代金融的兴起,人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现实原则不再起作用。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耐心、努力和真正的生产率提高才能带来回报的传统价值观也被抛弃。因为在金融世界里,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在如今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和公司只要掌握合适的关系和技术,或者抓住最佳的时机,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惊人的回报,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只是传统经济中的一个零头。在现代经济的各个方面,我每天都见证着各种各样的奇迹。在华尔街,公司“狙击手”通过快速买卖整个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在消费者文化中,连环再融资者和兼职“炒房”者似乎躺着就能赚到大笔钞票。在政治的世界中,美联储长期保持极低的利率水平,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重塑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梦想寄托在房地产泡沫上。到了21世纪初,整个美国社会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新观念:即时回报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远远优于那些需要努力和耐心才能获得回报的途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的金融化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本质。金融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高的回报,同时极力避免任何低效率的因素(比如努力、社会责任、社会规范等),因为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我们获得回报的速度。
当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化拒绝承认现实原则的存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纵观人类历史,任何试图通过金融板块将快感原则制度化的社会(这种潮流曾经一起又一次地出现过)最终都走向了灭亡。当世界经济被金融板块所主宰时,我们不仅会看到泡沫产生和破灭(或者其他形式的修正过程)的循环周期,还应该注意到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更微妙的、更深层次的伤害。当金融板块占据整体经济活动的很大份额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把资源从其他板块抢走,这些板块包括一些对人类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核心板块,比如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美国作为世界上金融板块规模最大的国家,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流向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板块(比如道路、能源研究、教育),而是流向一些完全投机性的资产(比如CDO和掉期交易)。虽然这种资本流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模更大、复杂度更高的经济体的融资需求,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更真实的、更不健康的驱动力:现代金融为个人和公司提供了实体经济无法提供的高回报率。
资本并不是唯一被金融板块抢走的资源。由于金融板块能提供高额的回报,各行各业很多最聪明的优秀人才离开了自己原有的职业,转而投身金融领域。事实上,这些人的才华和智慧是极为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本应获得更好的配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板块的工资与其他职业相比上升幅度更大(现在金融板块的工资比其板块高出50%)。 [25] 与此相呼应的是,大学毕业生中去华尔街就业的人数比例上升幅度同样巨大。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专业的毕业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上,这些充满智慧的年轻人应该进入一些对实体经济起突出作用的核心领域,比如工程、医药、研究等;如今,为了追求个人的即时回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金融板块就业。 [26] 国际清算银行两位研究金融板块扩张效应的专家斯蒂芬·切凯蒂和埃尼斯·哈鲁比这样写道:“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大量被金融板块抢走。那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那些在另一个时代中会以征服癌症或者飞向火星为职业目标的人才,如今却以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为人生理想。” [27] 面对这样的现象,很多保守派的经济学家甚至也开始担忧。虽然这些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总体上支持通过市场来分配人才资源,但他们也同意金融板块确实已经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扭曲。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曾这样写道:“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才放弃硅谷的创业机会,而成为华尔街的高频交易员。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反对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通过自身的才华致富,但是我们应该设法保证他致富的途径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益。” [28]
在这里,我认为曼昆提出的“以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益的”途径致富的理念非常重要。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个人和公司通过提供某种特定的商品和服务获得回报,而回报的水平应该恰好可以鼓励他们继续产出这种服务或商品。因此,脑外科医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是因为成为优秀的脑外科医生需要很多的技巧、勇气,还需要事先在大学教育阶段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我们降低脑外科医生的工资,就没有人愿意承担上述风险并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如果脑外科医生的薪酬过高,则会有过多的医学院毕业生想成为脑外科医生,于是脑外科领域就会出现人才过剩的现象,在竞争的压力下,工资会随之下降,而脑外科医生的职业也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所有市场一样,拥有自我修正的功能。通过这种功能,市场可以自动以最高的效率分配人才(或者其他资源)。正因如此,我们通常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较好的设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看到,金融板块不仅对劳动力市场施加了扭曲性的影响,也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因如此,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相信市场是全知全能的。简言之,金融板块回避了市场的正常修正机制,获得了过高的利润,不管是金融板块提供的服务,还是它们承担的风险,都不能证明这种过高的利润是合理的。
当然,金融板块并不是唯一获得暴利的。在任何经济中,都难免会有一些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通过某些不正当的优势(比如垄断和内部信息)来获得高额的工资或利润。他们所获得的薪酬或利润远远大于自由市场应该提供的水平,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暴利。经济学家将这种被某些板块攫取的剩余价值称为“租金”。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任何板块的寻租行为都比不上金融板块的来得严重。几个世纪以来,金融板块的从业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暴利,也就是说金融板块所获得的回报远超自由市场应该提供的水平,它们获得的利润与它们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不匹配的。金融板块获得暴利的途径包括:通过政治上的游说行为制造监管方面的漏洞,并创造各种极度复杂神秘的技术和手段,确保外人无法理解和监督他们的经营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投行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还和其他行业相当,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金融监管的放松和各种金融技术的飞速发展,投行经理的中位数收入迅速超过了其他行业,达到了其他行业的7~10倍。我相信这样的变化绝不是巧合 [29] )。随着金融板块剩余价值的飞速增长,金融板块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对实体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扭曲效应。大量资源被这个黑洞夺走,流出了其他板块。然而,如果将这些资源保留在原先的板块中,原本能产生更高的社会生产率,可惜的是,这些板块却不能在金钱上提供足够的回报,因此无法与金融板块进行资源上的竞争。
寻租行为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行为。因为大量人才和其他资源流入了金融板块,金融板块拥有了其他板块无法匹敌的优势。金融板块拥有大量的创新者、企业家以及善于游说的政客,这些资源保证了金融板块总是能找到新的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继续获得暴利租金。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金融板块在规模、就业人数以及利润方面持续增长,而非金融板块却出现了日益凋敝的趋势。在美国,目前制造业板块仅占整体经济规模的12%左右,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比例几乎达到了25%。 [30] 目前金融板块占美国整体经济规模的8.4%, [31] 几乎是其历史规模的3倍(在英国,金融板块同样展现了空前的繁荣。目前制造业板块仅占英国国民经济的12% ,是30年前制造业板块相对规模的一半。 [32] 金融板块增长的速度几乎是其他经济部门的3倍 [33] )。
由于下面将会谈到的原因,金融板块和其他板块相对规模的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历史上来看,制造业所提供的中等收入岗位远远多于金融板块。健康的制造业板块可以不断发展出新的科技,并通过外溢效应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促成全方位的经济增长。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金融板块却会产生一种逆向外溢效应,即将人才和其他资源从其他板块抢走。此外,制造业板块的波动率也远远小于金融板块。虽然制造业板块的失灵也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然而金融板块的失灵却可能将整个经济完全摧毁。由于金融板块能提供惊人的高额回报,它很容易催生各种风险巨大的投机行为,导致泡沫出现和循环周期被破坏。在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以下情况:切凯蒂和哈鲁比研究发现,一旦经济中金融板块所占份额超出了某一水平,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34] 因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扩大制造业板块的规模,同时缩小金融板块的规模。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却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我们任由制造业走向凋敝,却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手段鼓励金融板块的增长(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谈到,金融板块是目前美国经济中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最受政治保护的板块)。同时,我们还应该谨记这样的事实:很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保持着比美国大得多的制造业规模。在德国,有21%的经济产出来自制造业,而金融板块仅贡献了经济总产出的4%。在韩国,制造业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高达31% ,而金融板块仅贡献了7%。甚至在意大利,制造业的相对规模也超过了美国:意大利的制造业贡献了经济总产出的17% ,而金融板块仅贡献了5%。 [35]
从根本上说,过度膨胀的金融板块带来的最大风险不是对资源和人才的错误配置,也不是过高的波动率,而是对整体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随着金融板块的扩张,金融板块的思维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思维模式。即使在非金融板块的公司中,管理人员也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金融方面。如今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一名首席金融官,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种头衔。首席金融官的工作职责包括投资者关系,即在金融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市场使者中管理和保持公司的良好形象。通过向管理者提供以股票为基础的薪酬,几乎所有公司都将管理人员与金融市场直接绑定在一起(截至2000年,由于公司普遍将向管理人员发放股票期权作为薪酬的一部分,美国CEO的平均薪酬已经达到了员工中位数收入的400倍;而在20世纪70年代,CEO的薪酬仅为员工中位数收入的20倍。 [36] )
同样,金融工程也成为公司战略的标准化组成部分。所谓金融工程,是指利用股票回购等金融技术提升公司的股价。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繁荣期,很多美国公司的股价迅速上升,而这些公司又以自己的股份作为筹码收购其他的公司。当时的美国在线公司是一家互联网新贵,公司的营业收入只有50亿美元,而公司的股价高达1 750亿美元,美国在线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作为筹码收购了时代华纳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当时的利润是270亿美元,然而股票市值却只有美国在线公司的1/2。 [37] 到了世纪之交,一半以上的大公司并购项目都是以股票作为交易筹码的,然而仅仅在10年以前,以股票收购其他公司的行为还是闻所未闻的。 [38] 当然,很多股票市值惊人的公司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空中楼阁: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中,很多既没有产品也不产生利润的新兴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的帮助下被成功出售。狂热的消费者愿意花数亿美元来购买这样的公司。在被华尔街精心设计的公开上市过程中,这样的公司甚至可以卖出数十亿美元的高价。经济的更大份额(更多的工资、更多的销售额、更多的总价值)被互联网板块所占据。在互联网板块中,经济价值的基础不再是生产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金融市场上所谓金融工程的抽象活动。
到了21世纪初,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膨胀,美国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模式。消费者用不存在的财富继续他们追求自我的消费行为(在心理学上,我们知道房价的上升会带来财富效应。所谓财富效应是指,即使实际收入并不增加,只要消费者知道他们的房屋在升值,就会扩大消费支出。在财富效应的影响下,美国的消费支出达到了每年4 000亿美元。 [39] )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手段人为操纵股价。(2003—200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的股票回购规模增加到原来的4倍。 [40] )而在华尔街,那些本可以成为科学家的投资银行家正充分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进一步放大这些并不存在的财富。比如,华尔街发明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称为“二次合成债务抵押债券”。二次合成债务抵押债券由两个或多个其他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抵押的CDO构建而成,通过购买这种产品,投资者承担更多的借贷风险,同时也会获得更高的回报。比二次合成债务抵押债券更具创造性的是所谓的合成CDO产品。通过购买合成CDO产品,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CDO产品的价格变化获利,但并不需要真正持有那些CDO产品。有了合成CDO产品,任意数量的投资者就可以同时对同一种证券的价格进行投机,也就是说,大量投资者可以同时对抵押物(同一处房产)的价值波动进行投机。通过这些金融创新,华尔街创造了比实际房地产市场规模大许多倍的房地产相关的财富。此举使金融板块本身也被金融化了。已故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曾经指出,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进程中,老一代金融家是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比如铁路、石油管道、工厂以及工业系统的其他部分)来致富的。然而,明斯基认为,如今金融业的重点已不再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发展,而是投机行为所产生的快速回报和交易利润”。 [41] 金融业不断地投资于金融业本身。不可持续的快感原则如今变成了一门科学。冲动的美国走上了不断加速的新轨道。
然而,幻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退。冲动的社会及其最主要的引擎——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最可怕的地方便在于,它们看起来越是欣欣向荣,实际上就越是不可持续。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这场游戏的大玩家们就已经看到了大厦将倾的前景。在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投行中,交易员们常常将这些新证券称为“垃圾玩意儿”“怪物”“核武器浩劫”“迈克·泰森的重击”,他们也早已预见到“次贷要垮”的前景。然而,这些投行不仅继续向客户出售这些有毒的债券,甚至还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准备从垃圾债券的垮台中获利。这种现象虽然极不道德,却并不令人吃惊,毕竟金融市场始终以追求高回报为最大目标。这些新金融产品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在某个时间或地点崩溃,并对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然而短视的华尔街只重视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严重的社会影响。当有人对这些不合理的交易进行质疑时,华尔街的交易员和管理人员常常以一句首字母缩写的暗语作为回答,他们会说“IBG YBG”,意思是“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至于他们离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想必这些人并不关心。待我赚够钱后,哪怕洪水滔天。 [42]
当赌博者的运气不好、不断输钱时,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行为,这种行为被称为“损失厌恶”。损失厌恶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长期进化出的一种心理特点,因为我们习惯了物资匮乏的环境,因此任何形式的财产损失都会让我们产生本能的厌恶。在一些针对赌博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被试对损失和盈利的认知是非常不对称的,即使损失和盈利的金钱数目完全一样,被试的行为却相当于将损失视为盈利的两倍。 [43] 正是因为损失厌恶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21点玩家常常会在一手牌输掉之后把赌注翻倍继续玩下去,股票交易员也常常迟迟不愿抛掉手中亏损的股票,直到股价完全触底。而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时,房产所有人宁可继续赔钱也不肯以低于买入价的价格卖掉手中的房产——2006年,这样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位在拉斯韦加斯从事了40年房地产业务的资深人士弗洛伦斯·夏皮罗最近这样告诉我:“突然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没法把房子卖出去了。” [44] 最奇怪的是,很多“炒房”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现实,房地产经纪人居然需要对客户进行劝说和解释,告诉他们几个月前的巨额财富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夏皮罗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当时我们需要反复劝说我们的客户。我的一位客户跑来找我。他手上有12套房屋。他一直通过买入并转卖房屋赚钱,而现在这12套房子全砸在他手上了。我对这位客户说:‘没办法,市场已经停滞了。’”
当房地产市场率先垮塌时,整个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极强的损失厌恶心态,正是这些非理性的反应把危机对经济的伤害继续大幅放大。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公司利润的疲软,陷入恐慌的CEO启动了大规模的股票回购项目来挽救本公司股价。200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将净利润的62%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2008年,这一比例升至89%。 [45] 虽然股票回购计划有助于公司稳定股价,并保持高管的薪酬不受太大的影响,但这种做法却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导致这些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本与恶劣的经济环境做斗争。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曾提到过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拉佐尼克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很多最后需要联邦救助或外国投资者救援的公司,在危机开始之前进行了大量股票回购,从而耗尽了手中的现金储备。2007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导致整个美国市场陷入了自由落体状态,然而就在破产当年和破产前一年,雷曼兄弟公司刚刚花费了50多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同样,在危机中全面崩溃的两家拥有政府支持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自2003年以来总共花费了1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 [46]
金融板块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从自己制造的危机中脱身,股票回购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了抵消它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损失,很多投行对石油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行了大量的投机行为。虽然这种“对冲风险”的行为帮助投行减少了部分损失,但这些行为同时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在经济危机中失去了工作,还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食品和汽油开支。尽管这些金融机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在危机中垮台的命运。这时,它们又打出了一张制胜的金牌:它们声称由于自身规模过大,对经济的重要程度过高,政府不可以让它们垮台,必须向它们提供援助。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华尔街的大鳄们进行救助。这在事实上导致这些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高管们)逃避了很多以净化市场为目的的监管,而这些监管手段本应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对上述高风险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整个经济陷入了一种极为荒谬的状态,这仿佛是一场权力与人性的对决实验——而这场实验的结果正如我们预测的一样悲观。在经济的方方面面,蜥蜴脑都取得了绝对的掌控地位。
就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经济金融化所伴随的巨大风险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不仅公共债务和个人债务水平同时飙升,而且大量资本从生产制造业和其他“硬产业”流向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尤其是离岸投资活动)。这为英国的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却对英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整个英国经济出现了资源紧缺的状态,不仅包括金融资源的紧缺,还包括人才和智力资源的不足,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受到了美国的挑战。1904年,在一次针对英国银行家的演说中,曾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以严厉的措辞总结了英国面临的困境:“银行业并不是我们经济繁荣的制造者,相反,是经济的繁荣成全了银行业的发展。因此,银行业不是我们财富的来源,而是我们财富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资本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如果英格兰仅仅扮演“投资证券囤积者”的角色,我们是不可能继续生存和繁荣的。 [47]
然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世界主要的后工业化经济体似乎仍然铁了心拒不接受上述教训。金融板块仍然是美国经济中的主导性板块,而且主要金融机构的地位甚至比从前更加稳固。美国金融业的集中程度不断上升,12家超大型银行(包括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掌握了美国银行总资产的2/3以上。 [48] 与此同时,金融板块的蜥蜴脑思维继续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起着塑造作用。追求高回报率已经成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从体育教练到大学校长,都选择在各种工作岗位之间频繁跳槽,以追求最高的职业回报率。美国的结婚率持续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继续保留追求更好伴侣的可能性。商界更是完全被金融的思维模式锁定。公司CEO的平均就职年限已经下降到了5年;而在20年前,CEO的平均就职时间是9年。 [49] 以股票为基础的薪酬模式仍然是商业界的常态,股票回购策略和其他金融工程手段也继续大行其道。根据拉佐尼克的计算,2001—201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总共在股票回购上耗费了35 000亿美元的巨资——大约相当于美国政府为赢得二战所花费金额的3/4。 [50] 上述现象都是冲动的社会的典型症状——由于我们的经济完全围绕追求高速回报的欲望运转,从而越来越无法产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不仅完全拥抱了金融板块的这些特征,甚至将这些特征完全吸收,化作了自我的一部分。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继续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极力追求最快的回报,而且我们对这种追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无动于衷。消费者的品性和华尔街的性格日益趋同,我们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冲动短视。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对我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让我们看到投资银行家和公司“狙击手”式的行为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因此华尔街反而成为消费者学习的榜样。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上文提到过的那位曾在拉斯韦加斯担任房地产经纪人的托德·米勒开始从事一项全新职业:银行和被银行没收房产的房主之间的联络人。这项新工作经常要求米勒把来自银行的坏消息传达给即将被赶出自家房屋的房主们。米勒告诉我说,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米勒接触到的许多房主都表现出对违约的愧疚和痛苦。米勒说:“这些房主常常会邀我进屋,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很多人因为违约不能支付房贷而痛哭流涕。他们觉得非常羞愧。”然而,米勒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当他拜访那些即将被赶出自家房屋的房主时,经常看到他们家里布满各种昂贵的装饰,而这些东西都是用股权提取获得的现金来支付的。这些房屋的车道上常常停着一辆甚至两辆崭新的汽车,院子里摆满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用品。而且这些违约的房主中也很少有人再表现得痛苦不安了。米勒说:“现在大家反而开始吹嘘自己违约的情况。我曾经在一家健身房中听到一个人和朋友的谈话,那个人说:‘我已经快3年没有付过一毛钱的房贷了,银行马上就要没收我的房子,不过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我通过向银行再融资已经获得了5万美元的现金。’”当米勒谈到这样的情况时,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违约不付房贷而感到羞耻了。‘那不是你的错。’‘那是银行的错。’诸如此类。欠债不还曾经为社会习俗所不容,还不起钱曾经是一个人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而现在呢?大家再也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还不起钱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了。”
[1] Interview with author.
[2] Interview with author..
[3] Interview with author..
[4] Leith van Onselen, “Ireland, the Greatest Property Bust of All,”Macro Business ,April 8, 2013, http://www.macrobusiness.com.au/2013/04/ireland-the-greatest-property bust-of-all/.
[5] Matthew Benjamin, “Bond Traders Who Gave Bush a Pass May Ambush Obama or McCain,” Bloomberg, Aug. 10, 2008,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 chive&sid=ayrMJ4R.bmLY&refer=home.
[6]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4.
[7] Brian J. Hall, “Six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Equity-Based Pay,” NBER Working Paper 9887, July 2003, http://www.nber.org/papers/w9887.pdf?new_window=1.
[8] Ben Heineman, Jr. and Stephan Davis. “A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2011. http://www.ced.org/pdf/Are Institutional-Investors-Part-of-the-Problem-or-Part-of-the-Solution.pdf.
[9] Ibid., but see also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 p. 40, who argues that it is from four years in 1960s to four months today.
[10] “The Short Long,” speech delivered by Andrew G. Haldane and Richard Davies.
[11] “Shooting the Messenger: Quarterly Earnings and Short-Term Pressure to Perform,”Wha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uly 21, 2010, http:// 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fm?articleid=2550.
[12] G. Polsky and A. Lund, “Ca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form Cure Short-Termism?”Issues in Governance Studies 58, Brookings, March 2013.
[13] “Shooting the Messenger.”
[14] Google Inc. (Nasdaq-Goog), graph, Google Finance, https://www.google.com/f inance?cid=694653.
[15] Interview w.ith author.
[16] “A National Conversation o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panel discussion, Wilson Center, March 28, 2012, 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regaining-americas-compe titive-edge.
[17] Gustavo Grullon and David Eikenber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Stock Repurchases?”Bank of America and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5, no. 1 (Spring 2000),http://www.uic.edu/classes/idsc/ids472/research/PORTFOLI/JACFSU~1.PDF.
[18] Patrick Bolton, Wei Xiong, and Jose A. Schienkman, “Pay for Short-Term Performance: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Speculative Markets,” ECGI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79/2005, April 2005,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91142.
[19] Al Lewis,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Restate Earnings in 2005,”Denver Post ,Jan. 2, 2006, http://blogs.denverpost.com/lewis/2006/01/02/record-number-of-companies restate-earnings-in-2005/75/.
[20] Interview with author.
[21] Bethany McLean and Andrew Serwer, “Goldman Sachs: After the Fall,”Fortune Nov. 9, 1998, http://features.blogs.fortune.cnn.com/2011/10/23/goldman-sachs-after-the fall-fortune-1998/.
[22] Bethany McLean and Joe Nocera, “The Blundering Herd,”Vanity Fair , Nov. 2010.
[23] “Home Equity Extraction: The Real Cost of ‘Free Cash,’” Seeking Alpha, April 25, 2007,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33336-home-equity-extraction-the-real-cost-of-free-cash.
[24] Interview with author.
[25] Sameer Khatiwada,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Prof 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Digital Commons@ILR,Jan. 1, 2010,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01&context=intl;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9, 2012),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2/11/22/qje.qjs030.full; and Thomas Philippon, “Are Bankers Over-Paid?”EconoMonitor, Jan. 21, 2009, http://www.economonitor.com/blog/2009/01/are-bankers over-paid/.
[26] “A Paradigm Shif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Speech by Lorenzo Bini Smaghi.
[27] Stephen G. Cecchetti and Enisse Kharroubi,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28] Gregory N.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 3 (Summer 2013).
[29] Kevin J. Murphy, “Pay, Politic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 edited by Alan S. Blinder, Andrew W. Lo, and Robert M. Solow.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30] U.S. Chamber of Commerce Foundation, “Manufacturing’s Declining Share of GDP Is a Global Phenomenon, and It’s Something to Celebrate” March 22, 2012, http://emerging.uschamber.com/blog/2012/03/manufacturing%E2%80%99s-declining-share-gdp; “U.S Manufacturing In Contex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 U.S. government website,http://manufacturing.gov/mfg_in_context.html.
[31] Justin Latiart, “Number of the Week,”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 10, 2011.
[32] Adam Mellows-Facer, “Manufacturing a Recovery,”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Parliament.uk, http://www.parliament.uk/business/publications/research/key-issues for-the-new-parliament/economic-recovery/modern-manufacturing-and-an-export-led recovery/.
[33] Stephen Burgess, “Measuring Financial Sector Outpu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K GDP,”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2011 (Sept. 19, 2011),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quarterlybulletin/qb110304.pdf.
[34] Cecchetti et al.
[35] All finance shares at L. Maer, et al., “Financial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the UK Economy” House of Commons, England, August 2012, p4 http://www.parliament.uk/brief ing-papers/sn06193.pdf; all manufacturing shares at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of GDP),” The World Bank at data.world 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36] Lydia Depillis, “Congrats, CEOs! You’re Making 273 Times the Pay of the Average Worker,”Wonkblog , Washington Post , June 26,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6/26/congrats-ceos-youre-making-273-times-the-pay-of-the average-worker/.
[37] Ahmed Abuiliazeed and Al-Motaz Bellah Al-Agamawi, “AOL Time Warner Merger:Case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SlideShare, http://www.slideshare.net/magamawi/aol-time-warnercase-analysis.
[38] A. Rappaport, et al., “Stock or Cash: The Trade-offs for Buyers and Seller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Nov.-Dec. 1999,p. 147.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law/pg/offer/llm/iel/mas_sample_lecture.pdf
[39]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Dean Baker at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40] 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1] H. Minsky, in E. Tymoigne and R. Wray, The Rise and Fall of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 (Oxford: Routledge, 2013).
[42] “IBG YBG,” review of Jonathan Knee, The Accidental Investment Ban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n Words, Words, Words , http://wordsthrice.blogspot.com/2006/12/ibg-ybg.html.
[43] Yexin Jessica Li, Douglas Kenrick, Vladas Griskevicius, and Stephen L. Neuberg,“Economic Decision Biases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How Mating and Self Protection Motives Alter Loss Aver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no. 3 (2012), http://www.csom.umn.edu / marketinginstitute / research / documents /HowMatingandSelf-ProtectionMotivesAlterLossAversion.pdf.
[44] Interview with author.
[45] 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6] William Lazonick, “Everyone Is Paying Price for Share Buybacks,” FT.com,Sept. 25, 2008, http://www.ft.com/intl/cms/s/0/e75440f6-8b0e-11dd-b634-0000779fd18c.html#axzz2r21JdHWo.
[47] In Kevin Phil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2006), p. 312.
[48] Richard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A Proposal for Reform Before It’s Too Late(With Reference to Patrick Henry, Complexity and Reality)
[49] “Get Shorty,” lecture given by Andrew Haldane for the Sir John Gresham annual lecture, 2011. Cited at Financial Services Club Blog http:// thefinanser.co.uk/fsclub/2011/11/get-shorty-andrew-haldane-speech.html.
[50] Eric Reguly, “Buyback Boondoggle: Are Share Buybacks Killing Companies?”The Globe and Mail , Oct. 24,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rob magazine/the-buyback-boondoggle/article15004212/.

每年3~10月的每个周六,波特兰市西部都会举行农贸市场活动。在这里,访客们可以暂时远离短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的社会,品尝到生活的真正味道。在这样的农贸市场活动中,每一处摊位上都摆满了精心制作的各式手工美食,这也使得波特兰以“慢食品之都”而闻名。波特兰的农贸市场上还有很多本地著名的非商业化音乐表演:从绿色合唱团到迪吉里杜管,有人穿着苏格兰短裙骑独轮车,有人戴着达斯·维德头盔用风笛演奏《星球大战》的主题曲。就连来参加活动的人群也展示出该市极富参与精神的城市文化:头发花白的嬉皮士,充满自信的自行车骑手,浑身文身、表情真挚的非主流人士,当然还有向路人宣传各种内容的人,只要你愿意听,他们就愿意向你介绍和宣讲各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比如无家可归人士的收留问题,自行车道问题,同性恋婚姻问题,公司是否应该被当作公民来对待,是否应该强制提供含氟的饮用水等。在波特兰的城市文化中,对自我认知的高度重视是最鲜明的主题,这个城市中的现实生活就像电视剧《波特兰迪亚》中的情景一样。(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中,你恐怕都不可能见到自行车骑行地图不仅有英文版的,还有西班牙语版的、索马里语版的、尼泊尔语版的、俄语版的、缅甸语版的以及阿拉伯语版的。 [1] )波特兰整座城市的氛围是真诚的、稳健的、富有目标的,这里的人们惹了麻烦不会说走就走,而是会负责任地留下来,认真地处理善后工作。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波特兰文化的核心正是一种“说走就走”的精神。虽然这座城市的非主流文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然而对这座城市最热忱的非主流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别的城市搬来的移民,他们为了逃离美国不平衡的主流文化而抛弃从前的生活搬来波特兰居住。在上文提到的农贸市场上,我认识了艾丽。艾丽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告诉我说,之所以选择从洛杉矶搬来波特兰,是因为波特兰是第一座让她感到可以完全“融入”的城市。艾丽说:“我住在洛杉矶时,从不知道隔壁邻居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购买有机食品,是否支持同性恋婚姻。”在这里我还遇到了另一位移民斯蒂芬,斯蒂芬是一位学校老师,他说他之所以选择逃离中西部,是因为无法忍受那里保守的、不环保的思维方式。斯蒂芬说:“在这里我可以非常轻松自然地拉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的后院不使用杀虫剂’,我可以轻松自然地在食品店谈论垃圾的回收利用。”在这座充满新移民的城市,很多人都能讲出他们如何精心计划,从别的城市逃离至此。30多岁的马林对我说:“搬来波特兰是我们的一项战略决策。”马林和他的男友亚当在搬来波特兰之前曾经对6处备选地的情况进行过调查访问,他们表示:“我们想确保我们将搬去的地方是一个我们每天都想待在那里的地方。” [2]
波特兰并不是这些文化难民的唯一避难地点。在比尔·毕晓普具有先见性的著作《大归类》中,作者提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等城市也逐渐成为左翼人士的聚居地。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则集中在另一些城市和社区中,比如南加州的橙县、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以及伯明翰和休斯敦的城郊区域。人口的地理分布曾经主要由就业机会、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物质性的因素所决定。然而毕晓普说,如今人们却常常因为“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原因”而选择移民。这些原因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便利程度,与商业中心和体育馆的距离等。毕晓普告诉我:“人们在这方面变得精打细算。如今人们会像在餐馆里拿着一份菜单点菜一样,逐一比较各个城市的优缺点,经过严密的分析以后才最终选定自己的居住地点。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父辈从未想到过的。”用冲动的社会的术语来说,现在的人们会选择能最高效地提供最大精神回报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常住地。
我们可以选择的对象远不止城市和社区。如今,个人消费的目标日益变成寻找和创造一种可供我们自我表达的领地——包括能够强化我们的自我形象和向我们提供精神满足的地点、商品、经验、社交网络和人。我们日益强调什么是我们喜欢的,而对不喜欢的东西则立刻予以抛弃。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种个人化的过程可能意味着找到一处完美的社区,那里有战前手工式的简易房屋和垃圾回收桶,恰好完美地符合我们的偏好。对另一些人来说,个人化的过程可能意味着在网络上找到一群二次元的朋友,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与我们完全一致。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一种完全满足我们内心对人性深层次渴望的政治活动,也可以是一种帮助我们保持完美身体状态的自我监控技术。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对苹果或哈雷戴维森等品牌的迷恋,因为这些品牌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群体认同的方法。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一个24小时播放美食节目的频道,也可以是政治不正确的新闻节目,甚至可以是某种3D的游戏环境,在这种游戏中我们可以把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人砍成碎片。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点”,这些地点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基本欲望,即对能满足我们个人偏好的空间和体验的欲望。同样重要的是,上述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非常稳健和高效地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化的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当然是我们的胜利。今天的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根据个人的需要来选择与世界接触的渠道。这种伟大的自由正是消费者经济的基础。也正是这种伟大的自由让美国的消费者经济显得尤其迷人和可爱。然而,这种个性化的权力却成为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的市场越是能高效地满足我们的个人偏好,同时帮助我们规避一切我们不想面对的东西,我们就越像是使自己投身于沸水之中。在房地产泡沫的例子中,显然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超级高效的金融系统让我们能充分享受“成功”的生活方式,同时帮助我们规避一切令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比如我们根本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的事实。确实,我们追求个人化的大部分努力并不会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这些行为却可能产生一些我们不想面对的成本和后果。
比如,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寻找理想城市的问题。一方面,希望生活在与自己拥有类似看法、类似价值观或者类似时尚品位的人周围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需求,谁又会因此责怪那些寻找理想居住地的人呢?寻找一个完美的社区曾经那么困难,波特兰、奥斯汀、南加州的橙县那样的城市也许找到了某种创造共同价值观的完美渠道。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找到完全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整个国家逐渐失去了某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大归类”的风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地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1/4的美国人生活在深红或深蓝地区,所谓深红或深蓝地区是指某一党派在总统选举中能以超过20%的优势胜出的地区。然而,经过40多年的大归类,如今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与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聚居在同一社区,因此今天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住在这种所谓的“压倒多数地区”。 [3] (在波特兰及其周围的姆尔特诺默县,政治的平衡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不分伯仲,而如今民主党在这一区域能以45点的巨大优势赢得选举的胜利。 [4] )显然,这种民众政见方面的隔离趋势是导致美国政治中两党对立僵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还会再次讨论)。然而在社区的层面,这种隔离的趋势也降低了社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我们不必再掌握妥协和自我控制的艺术。在休斯敦、堪萨斯城或者伯明翰的城郊地区,自由主义者已经变成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同样,在左翼人群聚居的城市——如麦迪逊、奥斯汀和波特兰,保守派的声音也逐渐销声匿迹。虽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轻松的、舒适的生存环境,却也让我们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某种活力。波特兰地区一位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经济学家乔·科特赖特说道:“由于我们能够轻松地选择自己的邻居,我们失去了与不同背景的人们接触的机会,因此也就无法接触到那些与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人。”
对个性化生活和自我形象的强烈追求导致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本,政治两极化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对个性化的强烈追求会产生巨大的风险,然而这种风险表面看来却是非常微妙的:我们越是将自己闭锁于完全个人化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中,就越难以接触和接受任何我们不熟悉的、不符合我们偏好的东西。然而有一个冰冷的事实一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社会面临的某些最大的挑战既不是个人化的,也无法被个人化定制。相反,这些东西是固有的、集体的,并且常常是令人不快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耐心,必须包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必须愿意妥协和牺牲。简言之,社会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不美好的、不高效的东西,然而以欲望驱动、一味追求高效率的冲动的社会却不断地劝说我们回避这些东西。
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本次金融灾难结束之后,我们本应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通力合作,努力改变我们的金融体系,以及对金融体系的问题持放任态度的腐败的政治体系。事实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进一步抛弃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态度,将自己更深地封闭于个人的生活之中,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化的自我成为躲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我们的社会不断赋予每个公民更多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力,却几乎从不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些权力,这无异于为社会成员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市场不断向我们提供更大的个人权力,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广泛的社会中抽离,不用去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问题。这样的趋势明明是危险的,我们却无忧无虑地相信所谓“市场的智慧”,认为市场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东西,因为效率市场的经济理论正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这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标志性理念:每个人都只应该为自己而活。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大隔离”的趋势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大约200年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已经指出,自从美国人逃离了欧洲文化的严密控制,他们就不断受到个人主义的诱惑,希望可以“离开广泛的社会而只关心自己”,只关注个人的追求和目标。而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是因为大家都理解社会是取得个人利益的必要途径。务实的美国人认识到离开社区的帮助,个人的利益很难实现,因此他们选择继续保持与社会的接触,“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盟似乎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托克维尔写道:“因此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何时应该牺牲部分个人权力来拯救其他人”,正是这样的品质保证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始终充满活力,富有生产力。 [5]
然而,托克维尔这种“理智自我利益”的乐观想法是以一个大前提为基础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认同,个人的利益与整个社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过,随着消费者经济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大的个人权力(或者说至少让人们产生了个人权力不断提高的感觉),“与他人结成联盟”如今看起来似乎已经不那么有用了。同时,显然存在一种相反的作用力——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作用力诱惑着我们切断与他人的联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主要是由一些见证过战争和经济萧条的人创造的。这些人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深刻理解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明白适当的自我牺牲是保持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社会凝聚力的精神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成为那个年代左派和右派的共同信念。罗斯福新政中提倡的社群主义精神隐含了对自我牺牲的要求,然而随着自由主义的抬头,人们开始反对这种自我牺牲的要求(在肯尼迪总统发表“不要问”的演讲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嘲讽的口吻批评了总统的演讲:“质问公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政府是人民的主人和上帝,而公民只能是政府的仆人和信徒。然而对自由的人们来说,国家只是构成国家的所有公民的集合,并不是某种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神圣的东西。”)
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消费者经济向公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追求自我利益的机会,而且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再也不需要他人的协助和批准了。事实上,不管别人如何反对和批评,我们一样可以继续追求个人的目标。我们的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城堡。我们的房屋放弃了前庭、草坪等对外的结构,主要强调更大的内部空间、后院以及封闭的车库。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我们的经济已经无法向民众提供更多的个人实际财富,然而数字革命的兴起使追求个人自由的运动变成了社会文化的永久组成部分。追求个人自由本身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虽然经济危机多少打击了我们追求个人化生活的努力(现在,我们寻找理想生活城市的热情已不如2008年以前那样高涨),然而各种个人技术的发展却使我们可以继续以低廉的价格定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和无所不知的互联网,即使像我这样不太懂科技的消费者也仿佛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数据宇宙的最中心,我们能获得的资讯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是高度个性化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同事、家人、朋友联系。我们可以用从前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方式快速定位各种娱乐项目和购物场所。(我们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朋友正在哪间酒吧喝酒,并且能在导航软件的指引下迅速抵达狂欢的现场。)我们可以享受电脑算法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歌曲清单,也可以在不断翻新的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Vine(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服务系统)、Chatroulette(一个视频聊天网站)等网站上随时收看各种精彩的视频。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把自己的休闲时光(以及工作日中某个令我们不快的时段)定制为一种完全个人化、个性化的娱乐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各种高智慧的技术缓解我们的压力,填补我们的空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投身于我们真正的工作——自我表达——之中。
这种巨大的个人权力在一代人之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与个人技术的光辉前景相比,我们目前的这点享受几乎算不了什么。将来,智能手机将成为可穿戴甚至可植入的设备,互联网不仅会把我们连向数字化的目标,还能把我们连接到物理环境中的任何东西上。我们的汽车、房屋、家用电器、宠物、食品店货架上的各种商品、我们路过的各种商店都会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告诉我们它们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高科技算法通过统计方法分析出我们可能喜爱的商品,并尽最大努力劝说我们购买这些商品。在商场和机场,高科技的电子岗亭能自动察觉我们的存在,并立刻分析我们的购物历史,据此向我们提供量身定做的优惠信息。在派对上,电子化的标签可以显示每一位来宾的恋爱状态和职业地位,于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可以与哪些人调情,应该拍哪些人的马屁。 [6] 在一场谈话和另一场谈话的间隙(如果谈话比较无聊的话,甚至可以是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可以回复短信,查阅个人化的新闻推送,或者从街角的餐厅订购烤肉外卖(我们订的烤肉外卖很可能是由无人驾驶的小型飞机送上门的)。对于未来生活的形态,我们充满了各种乐观的想象和预测,似乎那将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以理性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生活:在任何的时刻,不管我身在何处,不管我和什么人在一起,我都可以精确地了解我的个人利益所在;我可以据此准确地判断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周围的人或者整个社会进行交流。有了这样的信息,人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将各方面的个人回报最大化。
也许,我们一直真诚地相信上述美好的生活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然而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对冲动的社会的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不能盲目相信市场对我们的承诺,因为在上一段旅途中,我们显然被冲动的社会严重误导,走上过一条非常危险和错误的道路。虽然不断放大的个人权力每一周都在奇迹般地持续增长,然而大量证据已经向我们证明:更高程度的个性化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理性地对待我们的个人利益以及社会的总体利益。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经看到软件设计师是如何诱使在线游戏玩家整日坐在电脑屏幕前,导致这些玩家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实际情况是,这种恶意诱导我们走上歧途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游戏领域。记者尼古拉斯·卡尔曾出版过一本观点尖锐而悲观的著作《浅薄》 [7] 。这本书中提到,所有身处数字化社会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卡尔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数字化环境太急于取悦消费者,因此对消费者的个人偏好过度迎合。整个互联网环境的组织形式就像一部巨大的网络游戏,在互联网的海洋中,每个网民都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正反馈机会。不论我们的鼠标点在哪里,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得新事物的奖励——这种新事物可以是文字、图片,也可以是其他的数字化对象。这种奖励的新鲜感(以及随之产生的神经递质释放)很快变得与信息内容本身同样重要。卡尔写道:“数字化的环境把我们都变成了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我们和小白鼠一样不停地按着面前的拉杆,希望获得社会或智力上的微小奖励。” [8]
更严重的是,对新事物的渴求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理解和处理已经获得的数据的能力。卡尔认为,由于获取新信息的行为本身已经变得和信息内容一样重要,我们的头脑因此产生了混乱,在我们已经获得的信息(比如一本我们已经下载却还没开始阅读的书)和想要获得新目标的欲望之间出现了冲突。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对新事物的期待和深层次地理解一个事物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心理过程,这两种心理过程之间的冲突使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这导致我们不能专心处理和吸收已有的信息。在这样的机制下,虽然我们消费了更多的信息,对信息的处理却变得更加粗糙和浅薄了。此外,有研究显示,任何常规性的行为最终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因此,一旦这种大量搜集、低效处理信息的模式成为习惯,就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永久性的结构改变。因此,即使我们离开数字王国走进现实世界,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深入地、高效地处理信息了。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越来越执迷于对新信息的挖掘,而不再有动力和能力对手头已有的信息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我们越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越来越无法区分哪些事物真正有意义,哪些东西只提供一种肤浅的刺激。面对复杂深刻的想法和问题,我们越来越力不从心。神经科学家乔丹·格拉夫曼这样告诉卡尔:“同时处理的任务越多,你就越轻率,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差。”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数字化革命事实上反而降低了我们理解自我利益的能力,人们不再知道何时应该适当牺牲个人利益以追求更长远的收益。
数字化的新工具不仅没有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变得更容易,反而成为我们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要理解这一现象并不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革命带来的问题只是商品经济产生的问题的最新版本。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商品经济就开始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有效的工具:智能手机、巨型SUV、加双倍熏肉的芝士汉堡王,所有这些迷人工具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让出售这些商品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当我们狂妄地滥用商业市场赋予我们的个人权力时,我们也许没有想到,那些居心叵测的公司向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并不是真的想向我们提供什么权力,它们唯一的目标是提高公司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的权力。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向消费者出售他们不想要的个人权力。然而在后物质主义的超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已经不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取决于商家认为卖什么最赚钱,我们想要某种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狂热地渴望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更多自由以及更多个人偏好。虽然我们不断强调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然而在每个产品周期中,促成更多、更强的消费者工具不断涌现的动力并不只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我们看到广告之前,在我们看到朋友手中的新产品之前,我们常常完全不了解这些新产品的性能和特点,试问我们怎么可能需要和想要一种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呢?因此,事实上每年大量流入市场的个人化权力主要反映的并不是消费者自身的需求,而是商业公司的需求:它们希望保持利润的机器不断运转,希望生产力不断提高,希望自己公司的股价永远不停地上涨。
显然,自从近100年前阿尔弗雷德·斯隆开始大规模生产“淘汰旧商品的需求”时起,上述现象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然而,随着数字化效率的提高,商家对利润的渴望不断升级,我们越来越多地以消费行为定义我们的生活和自我,市场和消费者自我之间的这种畸形关系已不再是“一种现象”,而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现象”。我们的商业机器不断生产过量的个人权力,就像农民过量生产谷物一样。因此,消费者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泛滥着各种过剩的东西:过量的马力,过量的像素,用不完的面积和数据内存空间,我们的身体无法消耗的快餐卡路里,过多的咖啡因,以及其他任何能被大规模生产的过量个人权力。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并不需要甚至并不想要这些过量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些权力,消费者的生活反而可能更美好——然而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这样的事实。只要过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它们就必须从供应链流入人们的生活,为了确保这一点,商家采用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颖而激进的市场营销策略,其中当然包括各种强制消费者更新换代的措施,除此之外,商家还越来越多地运用一些侵入性的手段:比如追踪我们访问过的网站,分析我们的购物历史,监控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商家通过这些数据预测我们的喜好和欲望,然后通过迎合这些喜好和欲望来追求它们的季度盈利目标。如今,有线电视公司已经可以向家庭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广告。一位电视公司的管理人员向我夸耀道:“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向养狗的人推送狗粮广告,向养猫的人推送猫粮广告,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家庭有3个孩子,我们就推送小型货车的广告。” [9] 因为大规模泄露用户数据而臭名昭著的塔吉特公司还曾因为另一项不光彩的举措受到过关注:塔吉特公司的市场推广系统能够根据少女的购物历史准确预测少女何时及是否怀孕,他们甚至能够比少女的父母更早知道少女怀孕的消息。 [10] 商家对消费者偏好的精心计算已经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中,我们的选择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决策,而是市场与我们合作的结果,在很多时候,市场甚至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我们的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市场就会与消费者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我们内在的渴求、我们对高效满足的不断追求会与商业公司对资本回报率的渴求完全同步。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市场与自我的完全同步会导致我们越来越习惯将自己视为我们私人宇宙的中心。随着每一个产品周期的出现,随着每一次产品的更新换代,自我表达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第二本能。自我表达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我们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负责任的公民,而变成了一群贪得无厌的自私鬼。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经济的健康程度,新的科技是否有用,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否可以接受,我们判断这些问题的标准变成了它们能否向我们提供更大的个人权力,能否让我们从一瞬间的自我满足和肯定直接跳转到另一瞬间的自我满足和肯定。
从文化的角度说,冲动的社会已经到达了终点:自我已经成了所有事物的中心,所有事物都必须围绕自我来运转。不择手段地谄媚讨好消费者的消费市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这样的现实,而其他板块也正越来越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现代政治中,一项政策和一位决策者的成功与否已不再取决于政策是否有用和高效,而取决于政策是否能够迎合选民的自我意识(你会想要和泰德·克鲁兹一起喝啤酒吗?你是否觉得希拉里·克林顿为人过于强势?)新闻不再报道对集体、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事件,而变成了一种完全迎合个人喜好的定制信息流。这种定制过程可能是通过某种个性化算法完成的,也可能是在我们随机点击各种能吸引我们眼球的头条的过程中自动完成的。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把这种新闻形式称为“每日自我播报”。甚至连我们的艺术也越来越少地去讨论深刻的、存在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少地去表现那些重要的、永恒的主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以个人认同为核心。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经发现,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当一个人看到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一本书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这个东西美不美、深刻不深刻”,而是“这个东西能为我做什么”。在丹尼尔·贝尔的时代,数字剪辑技术尚未出现。如今,数字剪辑技术已经把文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电视剧、歌曲、电影或图书——都转化成可以随意拼贴的美学碎片,人们可以随意心所欲地把这些碎片撕裂和重组,通过各种形式的混搭达到自我表达的目的。在冲动的社会中,所有文化都只是自我的工具和傀儡。随着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和自我创造,我们的自我在一刻不停地膨胀。
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个人化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只有我们熟悉的东西,只有与我们的自我相关的事物。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情况后,任何我们不熟悉的、与我们无关的事情都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和恐慌。陌生和差异让我们焦虑。他人的不同意见使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即使对最文明理性的公民来说,要保持社会的多样性都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妥协,同时也必然会引入一定程度的风险,而这些所谓的低效率元素却正是如今我们的消费者文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极力排斥的东西。然而,这些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低效率元素对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必不可少。这些元素是民主和社区的基础,而民主与社区这两种制度从定义上来说注定不是效率最高的。卡斯·桑斯坦(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曾提到过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者)认为,有效的民主文化必须包含某种混乱而尴尬的“不期而遇”,人们必须能够“接触到一些他们并不想接触到的东西,必须能够听到一些他们并不想听到的话题和观点,虽然这些东西常常令人不快”。 [11] 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随着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日益适应我们的偏好,人们越来越相信我们有权力躲避我们不想听到的意见,远离我们讨厌的人,避免其他各种形式的“不期而遇”。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民主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每个人都完全接受和认同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在那个时代,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求同存异的方法,比如,与别人礼貌地谈话时,我们可能会故意回避某些敏感的话题(如政治和宗教)。通过这类行为,我们成功保持了各类人群的共同价值基础,从而保证我们的社区和社会能够良好地运行。然而,如今任何稍微委屈自己的行为都被视作对自我表达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发现,与其委屈自己适应他人,不如只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这样我们就可以只接触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观点了。
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习惯。一旦我们不再能包容任何形式的差异,一旦我们开始在自己和与自己不同的人群之间制造实际和虚拟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桑斯坦和毕晓普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受群体心理学的影响,如果一个社区中的成员拥有非常相似的价值观,那么他们的观点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容忍不同意见的能力也会越来越低。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和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类似的群体中时,群体的肯定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更加自信。很多研究显示,对于大部分政治和社会问题,一个普通的个体通常并不会拥有非常强烈的观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比较和分析各种不同论点,因此也就无法得出非常明确和强烈的结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并不具有强烈的自信。于是,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常常倾向于把周围人的普遍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桑斯坦认为,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的多样化社区中,这样的心理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持有比较中立的观点”。换句话说,中庸的态度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本能。然而,在一个经过分类的、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似的社区中,通过不断赞同和肯定他人的意见,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并不需要认真的分析和思考,群体的认同已经足够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桑斯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信心越高涨,我们的信念就会变得越强烈。用桑斯坦的话说:“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因为团体的支持和肯定,人们的看法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因为当人们知道其他人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时,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自信。” [12] 而毕晓普认为,上述动态机制几乎在每一种高度趋同的群体中都会出现。不管是选民、同一间教室里的学生、陪审团中的陪审员,还是联邦法院的法官,在任何群体中,只要群体的多样性降低,人们的意见就会变得更加极端。 [13] 毕晓普说:“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方面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多样化的人群聚居在一起能让大家变得更加平和与中庸,如果持相同意见的人聚集在一起,则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和极端主义。多样化的社区能够限制群体的极端思想,而过于趋同的社区则导致不同人群间的分歧日益加剧。”
在政治领域,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在第八章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在社会化的世界中,个人越想保持自我,就越会对保持自我的能力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林奇是一位人类知识理论的专家。林奇认为,一旦人类失去了忍受不同意见的意愿,就失去了获得真正的自我认知的能力。当我们拒绝接受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时,我们不仅拒绝了这些具体的人,还拒绝了“他人”这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拒绝承认在自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受我们控制,也不依赖于我们的自我而存在。然而,林奇认为,他人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人不仅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帮助我们保证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还是我们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只有认识到自我之外还存在某种更广阔的东西,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是谁(更重要的是,理解自己不是谁)。在我们的消费者文化中,由于外界越来越努力迎合我们的偏好和需求,自我与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林奇说:“我们需要‘他人’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确定自我的界限,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自我的界限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断扩大。我们的自我不断膨胀,自我的领地也变得越来越广阔,于是对世界的兴趣渐渐等同于对自我的兴趣。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观念。因为世界总是比我们的自我更加宏大,世界比任何一个人的自我都更加广阔。我们越相信自己能够控制整个世界,就越会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洞穴中,被洞穴墙上的影子所愚弄。”过度的自我膨胀非但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反而削弱了我们的能力。林奇说:“我们变得巨大而脆弱,你懂吗?就像一个充满了空气的热气球一样。” [14] 这是冲动的社会所导致的另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社区的支持,然而,当我们不断地努力创造一个能完全反映我们自我身份的社区环境时,我们是否反而抹杀了那些定义我们个人存在的最重要的东西呢?
用热气球比喻不断膨胀却日益脆弱的现代自我是非常恰当的。事实上,个人化的过程其实意味着我们拒绝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而坚持让世界围绕我们个人的偏好运转,似乎控制和主宰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模式。然而,人类并非生来就是外部世界的主人。相反,我们是为了适应广阔的外部环境而生的。人类进化出体积更大的大脑是为了与其他人合作、协商和妥协;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外部环境从不主动适应我们的偏好和愿望。虽然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各种改善周围环境的技巧,然而能否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能否让自己和自己的预期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正是在不断忍受各种困难和失望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获得了力量、知识和洞察力,这些宝贵的东西不会因外部世界的艰险而磨灭,正是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让人类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人。
几乎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都理解和认同这一点:不接受逆境的考验,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坚强的、自给自足的个人——逆境是人格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然而,我们的现代文化却过分强调“个性”,鼓励我们回避一切形式的不快和困难。在我们冲动的社会中,消费者文化的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消费者文化尽一切努力说服大家,艰险、困难,甚至尴尬都完全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只有在一些特殊的自我提高的时刻,比如绳索训练和魔鬼腹肌训练时才可以出现)。不适、困难、焦虑、忍耐、压抑、拒绝、不确定性、模糊性,在冲动的社会中,这些不再是帮助人们成长、让人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的机会。相反,它们只是错误和低效率的代表,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修正这些错误,而修正的方式通常是更多的消费和更强烈的自我表达。
于是,我们再也不想为了一个包裹等上几天,我们希望任何商品都能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家门口。我们甚至愿意付费享受当天送达的服务。我们渴望亚马逊能够早日推出无人机送货服务,让我们订购的商品可以在30分钟内来到我们身边 [15] 。随着我们的社会系统能够越来越快地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完全忘记了还存在这样的可能:也许等待和忍耐才会让我们更加满足。等待和困难是高效率消费者市场的最大敌人,就像真空是自然的敌人一样。因此,虽然等待、困难、低效也许能塑造更坚强的人格,我们却没有耐心去等待这一过程的发生。对效率市场而言,人格和美德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的元素;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产量的提高和股价的抬升,而人格和美德却是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只要我们的社会能够产出更多自我表达、自我满足、自我提升的权力,我们就必须立刻使用这些权力,这是整个现代消费者文化最重要的隐含假设。因此,如今我们自我表达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自我不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由效率市场决定,由商业机器决定,由永远不知疲倦的资本和创新的循环决定。虽然这会让我们的自我变得越来越虚弱,我们却早已丧失了拒绝的能力。
当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更新的高效率来源时,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都知道,对个人的发展而言,社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在社区中,我们才能学习和吸收社会的规则和常识,为人际交往和取得成功做好准备。正是在社区中,我们理解了限制和自我克制的必要性,理解了耐心、坚持以及长期承诺的重要性,并将这些概念内化为我们价值观的重要部分。社区压力是社会限制个人短视和自私行为的重要的渠道。(用经济学家萨姆·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的话说,社区是“将社会义务转化为个人愿望的渠道”。)然而,社区不仅仅通过对个人的不当行为说“不”来完成上述任务。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我们逐渐发现自己的能力和长处。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作为公民和社会生产者的价值感。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我们不仅消费社会商品,还能通过生产社区所需要的东西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社区不仅能教育我们成为具有生产力的公民。在社区中,有较强社会关系的个人通常生活得更好。这些人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更加健康,也能够更快地从伤病中恢复过来,此外,他们患进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概率也低于普通人群。 [16] 研究显示,与社区联系紧密的人更快乐,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更高,即使这些人所处的社区并不富裕,或者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一规律也仍然成立。 [17] 事实上,在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因素中,社会联系甚至比金钱更重要。研究显示,定期参加社会活动(如志愿者活动、教堂活动、招待朋友、参加俱乐部等)能显著提高我们的快乐程度,其效果相当于把我们的个人收入增加一倍。 [18]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曾这样说道:“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在所有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变量中,对我们的快乐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社会关系的深度和广度。这一规律不仅在美国成立,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广泛适用。” [19]
可惜的是,虽然社会关系如此重要,在冲动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却未能很好地保护这种重要的财富。随着商业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很多过去曾十分紧密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或者被某种崭新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新的社会结构也许确实比传统的社会结构更好——即使在一些表面看来十分自由的社会中,传统社区也通常会压抑个人成长、个人实验以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然而,虽然新的社会关系希望赋予每个个体更多的主动权,让个体能够选择和控制自己与社会联系的方式,但它同时也导致了高昂的成本。社会关系逐渐成为消费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希望社会关系能够迎合个人的偏好和计划,我们不再把社区当作一种必需和义务,而认为社区应该适应个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当社区与我们的心情和偏好相适应时,我们才愿意参与社区的活动。这种空前的自由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我们能够全面控制自己发展社会关系的过程,我们有时会选择回避某些需要妥协的传统互动方式,而这些互动方式可能是将我们塑造为有用的、完满的个人的关键因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通过电子渠道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一项我们引以为豪的崭新的个人权力。从理论上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本应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然而,由于电子化交流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的限制——我们可以不断展示任何形态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表达任何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不成熟、不合适,多么平庸——这种个人权力可能稀释了社会交往的价值。
研究显示,如果人们可以长期在网上有效的交流,就会对线下的人际关系造成伤害。约瑟夫·格雷尼是VitalSmarts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人们的网络行为进行问卷调查。格雷尼告诉我们:“人们似乎完全清楚,许多重要对话不应该发生在虚拟的社交媒介上。然而人们似乎无法抵挡网络的诱惑,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便的渠道立刻释放自己的情绪。” [20]
我们希望通过网络交流建立某种我们需要的联系,然而由于网上交流过于容易,这种过度的方便反而会伤害我们试图建立的关系。即使网络交流是完全友善的,这种伤害也无法避免。社会学家和诊疗心理学家雪莉·特克花费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人们在数字网络上的交流情况。雪莉·特克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完全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如此频繁,任何短暂的失联都会让我们感到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没有人会因为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与他人联系而感到不安,然而在数字化的今天,如果不能随时随地获得反馈,人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适。在雪莉·特克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特克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时间轴完全坍塌的社交世界。大学生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给父母发短信,汇报各种微小的事项,一旦他们不能迅速获得回复,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如果情侣中有一方不能快速回复短信,很可能会导致分手的结局。如果在朋友圈给朋友的点赞不够及时,友谊常常因此走向尽头。今天,如果一位青少年不能立刻回复父母的电话和短信,很多父母就会拨打911报警——在数字时代之前,这种恐慌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数字化技术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权力,也提高了我们交流的效率,然而我们的世界却因此变得更缺乏安全感了。
如今,几乎所有的社交互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渠道来完成,然而在这个完全数字化的表面之下却潜藏着高效率所导致的不安全感。不论对何种类型的关系(爱情关系、家庭关系甚至职业关系)而言,数字技术的性质导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情绪悬念之中。数字化交流具有简短、非正式的特点,我们交流的内容常常是思想和情绪的碎片,只有更多的交流才可能消除其不完整感。因此我们总是在等待,希望知道故事的下一步进展。特克认为,数字交流的这种特点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的情绪尚未完全形成就已经被表达了。同时,交流和表达成了情绪的一部分,未被交流和表达的情绪被当作不完整的情绪。”换句话说,思想和情绪曾经主要是一种内在的过程,我们首先在内心完整地构筑起思想和情绪,然后才会去表达这些思想和情绪,然而,如今思想和情绪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循环的、公共的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循环的互动过程——这就产生了特克所说的“合作性自我”。与此同时,我们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完全私人的、自我满足的个体的能力。特克写道:“现代文化不再要求我们学习如何独处,也不再培养在独处状态下反思自己情绪的能力。”因此,虽然冲动的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我们却正在失去真正的独处能力。
在一种如此执迷于个人利益的文化中,我们却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这实在是冲动的社会最具讽刺意味的特点之一。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表面上过于热心、实质上却对我们进行冷酷操纵的消费者文化中,消费者无异于一群无助的羔羊,消费者文化一方面赋予我们绝对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我们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市场和商业机器。这极易导致一种矛盾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识,我们一方面高度自我膨胀,另一方面又被一种深层次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所吞噬。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主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不得不追求更多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作为补偿。然而,这只会让我们更加远离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使我们无法在人际关系的帮助下获得稳定的、完满的自我体验。
在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托弗·拉希把这种空虚的个人主义诊断为文化所催生的自恋主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身份从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我们丧失了很多技能,也丧失了对自我能力的认同,以及依靠自己改变世界的信心,而这两个元素是促成自信、安全、内在化的自我认知的重要元素。由于缺乏自我满足的内在生活,我们转而追求一些外在的替代品。我们越来越渴望其他人的认同。我们迷信专家的意见,沉醉于各种名人和成功的故事。我们极力追求社会地位和新鲜事物带来的即时快感。面对这样的需求,对机会和缺乏高度敏感的消费者文化迅速反应,向我们提供各种途径暂时性地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这些替代品如此精美迷人,我们渐渐对这种外部刺激上了瘾。于是我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发生了融合,最终导致了拉希所说的自恋文化的形成。
拉希的这种诊断是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恋症状。不仅就诊患者中这种症状变得更加普遍,在社会上的普通人群中,自恋同样变成了一种流行病。随着自恋症的流行,很多病态的心理症状越来越普遍,比如过度的自我膨胀,过于激进地追求自我提升的倾向,过度依赖外界认同的矛盾心理,以及认为自己的固有权力未被满足而产生的愤怒。虽然患有严重自恋人格障碍症的人是极少数,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一种或多种自恋倾向,自恋症发病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心理障碍(比如强迫症)。《自恋流行病》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琼·特文格和基思·坎贝尔的研究显示,自恋症在普通人群中增长的速度与其他公共健康问题(如肥胖)的增长速度一样惊人。
为什么自恋症变得越来越普遍?标准的解释主要着眼于文化和家庭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和文化都开始强调建立儿童自尊心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在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被灌输这样的信念:自己是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长大以后,仍然抱有一种不现实的、幻想性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在外部世界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认为经济因素也是造成自恋文化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自恋主义的核心是从本质上拒绝接受外界的限制,不久前,只有十分富有的精英阶层才有权力和机会拒绝外界的限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艰难很快就会让我们习得一种更加现实的自我认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然而特文格和坎贝尔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在过去的40年中,个人权力水平的飞速提升(包括技术、金融以及社会方面的权力),使得逃避现实约束的自恋主义在更广泛的人群中生根发芽。特文格和坎贝尔认为,造成自恋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宽松的消费者信贷的盛行。消费者信贷从两个方面促成了自恋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它使人们可以暂时逃避经济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度消费可以进一步加强人们的自我认同,使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大幅膨胀。特文格和坎贝尔指出,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革命和自恋主义文化已经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宽松的消费者信贷(换句话说,是某些消费者背负巨额债务的意愿和能力)使人们可以向自己和社会展示出成功的假象。”
当然,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信贷的标准。但是,随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技术的推出,自恋型人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廉价而高效的途径,使我们可以向世界和自己展示一幅虚幻的伟大自我的形象。随着自我追踪运动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监控、分析甚至在虚拟世界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卡路里的摄取到当下的心情,再到家庭和办公室的工作效率。这种自我追踪运动让我们能以一种所谓的客观视角来审视自己,然而这种行为本质上必然会鼓励进一步的自我迷恋和自我中心(技术怀疑论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将这些自我追踪者称为“数据恋者”)。我们越来越喜欢拍摄和展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明星般的自恋之爱。40多年前,拉希就曾经对现代化的生活做出了这样的描述:“电子图像成为生活方方面面的中介,在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表演,好像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被一台看不见的摄影机所摄录一样。我们似乎随时都在想象着有一群看不见的观众正在欣赏我们的表演,同时我们想象自己的表演影像会被存储起来,在未来的某一刻受到认真的检视。” [21] 然而,如今拉希这种带有含糊的妄想性质的比喻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标准运作模式。现在担任佐治亚大学心理系主任的坎贝尔说:“我们拍摄所有的事情。人们会拍下正在听音乐会的自己,而且自拍仿佛成了听音乐会的真正目的。从前人们的生活态度是享受当下,如今人们的生活态度变成了向人们展示我正在享受当下。很多时候人们的想法是:‘天哪,我必须赶快拍张照片,贴到社交网络上以获得回应。’”
的确,让别人看到自己日益成为人们取得个人成功和社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自我表达能够被他人所消费——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人在YouTube和脸书上传各种DIY(自己动手制作)的宣传片,而更厉害的人则选择参加商业化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这种节目的核心就是让普通人去做不普通的事情。在这类节目中,我们又一次成了生产者,然而我们的产出已不再是谷物、煤炭和钢铁,而变成了各种尴尬、凶暴、利己主义的表演,只要能抓住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球,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敢做的。真人秀节目源自上镜文化,又反过来为上镜文化添柴加火。真人秀节目是追求个性化之路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冲动的社会的实时编年史。在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冲动的社会的一切特点: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自恋冲动、观众追求快速直接的兴奋感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技术效率和金融效率的不懈追求。各种电视媒体之所以喜好真人秀节目,是因为制作这种节目的成本极为低廉:参与者常常不需要任何报酬(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真人秀节目获得暂时的知名度,并发展演艺事业),先进的录影技术使媒体可以轻松将数百小时的录影带剪辑成各种充满戏剧冲突的剧集。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追求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如何将市场进一步推向自我,又如何将自我进一步推向市场。
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真人秀节目的流行实际上将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幻想合理化了。这个核心幻想就是:自我是度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任何能扩大自我和吸引更多人关注自我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多么冲动、多么反社会,或者多么愚蠢)都是个人成功的标志。正在研究真人秀节目现象的坎贝尔说:“真人秀传递给我们的理念就是:只要我们表现得足够反常,足够令人讨厌,别人就会注意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明星。这种知名度不是基于个人的能力,甚至也不是基于个人的出身:这简直是最容易的出名方法。我想说的是,金·卡戴珊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她出名的方式实在是太聪明了,简直和帕丽斯·希尔顿一样。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这种名?” [22]
与此同时,真人秀节目还使我们看到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失败之处: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应该如何塑造独立可靠的自我。回顾美国历史,美国人民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DIY项目来定义和展示他们的自我:从共和国最初的日子开始,我们就是自己成就自己的个体,我们可以利用任何形式的文化元素(不论是最虔诚的宗教元素,还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元素)来塑造和修饰自我,我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我们最想要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创造过程有时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中撤离: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惠特曼等19世纪的美国作家都认为,自我实现有时需要个人脱离“广阔的社会和僵死的制度”,如爱默生所说,以更好地“接受个人目标的指引”。有时候,这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认为,当国家侵犯了个人的原则和信念时,人们应该收回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用梭罗的话说,这是一种“公民的反叛”。
然而,在这种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中,在讨论自我认识时,人们从来不会把自我实现和自我沉迷混为一谈,人们也从来不认为自我创造的过程应该允许个人从社会中完全抽离。事实上,对大部分19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社会是美国人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梅尔维尔和惠特曼都非常重视并强调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即使是梭罗抵制美国政治体制的行为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这个体制的热爱,以及把这个体制变得更好的愿望和决心。旧世界的等级制度将公民锁定在不同的阶层和位置上,并以此确立了每个人的身份。虽然美国人宣称我们已经从旧世界中独立出来,但事实上,作为来自旧世界的移民,我们从未正式拒绝过旧世界的社会人格概念和自我定义。比如,我们可以在美国流行的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中清楚地找到欧洲文化的基因。在这些小说中,自我创造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化过程:主人公会经历一个拒绝社会、试图独立行动的阶段,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变成更有智慧、更坚强的个体,从而能够以生产者的身份重归社会。社会化始终是这些个体的目标。并不存在仅仅以自我为目标的自我实现过程。 [23] 用黑格尔的话说,自我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发现一个“宇宙”,这个所谓的宇宙是指个人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耶鲁大学的艾伦·伍德曾经写道:在这样的冒险过程中,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通过“某种任性的行为或沉醉于某种任性的行为来完成,也不是通过培养某种个人特殊的个性和癖好来完成,而是通过发展一种完善的人格来完成,这种社会化的人格以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价值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24]
然而,今天我们对自我实现的定义与上述定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我实现意味着培养任性、个性以及个人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把上述特质视作个人成长的唯一途径。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是通过扮演社会化的生产者角色而出名的,也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默默努力,甚至连“努力”这一概念本身也不再受到尊重。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向我们的孩子传授这样的旧式价值观:个人的成功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延迟满足的毅力,需要控制自己冲动的能力。然而,如今当我们的孩子环视周围的社会,他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价值观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父母或祖父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保持着耐心,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热情,然而这些普通劳动者仍然像破旧的沙发一样被时代所抛弃,而投资银行家和真人秀节目明星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赚取了大笔现金。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难怪作弊会在高中和大学中日益盛行。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长期坚持录制各种自拍视频,他们虽然身处极为简陋的环境,却时刻幻想着能把数百万的观众点击量换成现金。布赖恩·罗宾斯拥有一家名为“超棒电视”的公司,这家公司在YouTube网站上开设了很多面向青少年及8~12岁儿童的频道。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罗宾斯曾这样说道:“如果你有机会和今天的孩子们谈话,你会发现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出名。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名。” [25] 确实,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这样,只要能获得免费的午餐,任何手段都可以。坎贝尔说,如果你问一位20岁的青年如何才能致富,你通常最可能听到以下三个答案:“一是我可以通过参加真人秀变成明星;二是我可以创立一家网络公司,并在一周内将公司销售给谷歌;三是我可以去高盛投行工作,这样老年人就会乖乖地把钱送给我。”坎贝尔说:“你看,这就是现在年轻人赚钱的三种途径。在这些人眼中,努力工作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不再对长期承诺提供任何奖励,也不再鼓励人们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这种冲动的社会培养出大批自恋型人格的个体并不奇怪。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商业高管尤其适合现代社会这种对快速结果提供高额奖励的商业文化。他说:“在这些CEO的努力下,我们拥有了很多高风险项目,而这些项目并不总是能带来高回报。更糟糕的是,这种高风险型人格通常还伴随着低道德标准的特质,这两种特点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人在流动性高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优势:在不断更换工作伙伴或者去新的社区生活的过程中,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的群体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因为自恋型人格的人拥有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这能“帮他们营造出充满自信的形象,这对面试很有好处。在很多与销售相关的领域,这种自信的形象也很重要。这和恋爱约会是一个道理。自恋型人格能够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是却不利于长期保持恋情。”不用说,自恋型人格对于消费者经济而言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格类型,因为消费者经济的目标就是利用人们永恒的不安全感、不满足感,以及对占有的渴望来牟利。用坎贝尔的话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最完美的消费者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的是焦虑、傲慢,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应得的消费者。你最希望看到这种同时拥有焦虑和傲慢的双重人格的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者经济也确实培养出了大批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利用人的谦卑赚到钱。”
[1] “Bike + Walk Maps,” Portland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City of Portland, OR,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39402.
[2] Interview with author.
[3] 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 (Boston: Houghton Mif f lin, 2008), p. 5–6;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
[4] “2012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table, Dave Leip’s Atlas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uselectionatlas.org/RESULTS/.
[5] Cited in Tom Murphy, “An Angel and a Brute: Self-Interest and Individualism in Tocqueville’s America,” essay for preceptorial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 St. John’s College, Santa Fe, NM, http://www.brtom.org/sjc/sjc4.html.
[6] Michio Kaku, “The Next 20 Years: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Telecom, and AI in the Future,” keynote address, RSA Conferenc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kmb16zSOY.
[7] 《浅薄》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8] 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W. W.Norton, 2011), p. 117.
[9] Kent Gibbons, “Advanced Advertising: Obama Campaign Showed Value of Targeting Viewers,” MultichannelNews, Nov. 13, 2012, http://www.multichannel.com/mcnbc events/advanced-advertising-obama-campaign-showed-value-targeting-viewers/140262.
[10] C. Duhigg, “How Companies Learn Your Secrets,”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 16, 2012.
[11] Cass R. Sunstein, Republic.com 2.0: Revenge of the Blog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12] Cass R. Sunstein,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5.
[13] Cass R. Sunstein, 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Oliver Wendell Holmes Lect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ited in Bishop p. 67.
[14] Interview with author.
[15] 这还远远不是技术革新的终点:沃尔沃的数字钥匙技术可以让网购者以它们的汽车作为送货和取货的地址。
[16] Putnam, Bowling Alone , p. 332.
[17]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linked to happiness and vibrant communities”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www.hks.harvard.edu/saguaro/communitysurvey/results4.html;This Emotional Lif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January 2010. http://www.pbs.org/thisemotionallife/topic/connecting/connection-happiness.
[18] In Putnam, Bowling Alone, p. 333.
[19] Ibid.
[20] Belinda Goldsmith, “Friendships Cut Short on Social Media as People Get Ruder: Survey,”Reuters, Apr 10,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4/10/us-socialmedia behaviour-survey-idUSBRE9390TO20130410.
[21]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p. 47.
[22]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3] James A. Good and Jim Garrison, “Traces of Hegelian Bildung in Dewey’s Philosophy,”in Paul Fairf ield, ed., John Dewe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arbondale, IL: Board of Truste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0).
[24] Allen W. Wood, “Hegel on Education,” in Amélie O. Rorty, ed., Philosophy as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www.stanford.edu/~allenw/webpapers/HegelEd.doc.
[25] Quoted by Ken Auletta in “Outside the Box,”The New Yorker , Feb. 3, 2014.
2011年年末,“占领华尔街”从美国扩展到了英格兰。英国一位刚刚获得律师资格的年轻律师(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在推特上用的假名是“占领旅馆”)发起了一场史上最不可能发生的政治活动:抗议新律师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这位抗议者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虽然我们自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法学院毕业生却发现社会上缺少适合我们的工作——至少缺少作为律师的工作。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成了助理律师,而不够幸运的人只能在酒吧工作。” [1] 这场抗议活动并没有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英国也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好,律师仍然是受人尊敬的好工作。然而这位抗议者的诉求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在后工业化国家,律师的就业市场呈现出饱和的迹象。在美国,虽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目前法学院毕业生与工作机会的比例大约为2∶1。 [2] 在英国,律师的工作机会更加稀缺:2011年,伦敦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师招聘数目严重小于申请这类工作的申请人数,申请人数和工作岗位数目的比例达到了65∶1。 [3] 同时,目前我们看不到情况将会显著改善的希望。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在尽最大努力大幅削减开支:很多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将各种低价值工作(比如索赔处理等工作)离岸外包至斯里兰卡和菲律宾。此外,即使最传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进行一项之前很少有律师曾经想到的改革:事务的自动化处理。通过一系列语义敏感性的搜索算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已经由机械自动化完成。比如,一个复杂的案件可能会产生数千页法律文件,以前律所需要组织一群工资很高的律师花几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这些文件;而现在,有了上述自动算法,机器只需要花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4]
律师界的这种变化只是高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就业状况的一个缩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能很快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法律算法——数量化法律预测算法。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可以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预测法律案件的审判结果,就像《点球成金》中通过统计分析预测棒球比赛的结果一样。 [5] 数量化法律预测算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在我们付给律师的律师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律师对未来的预测。根据现存的法律规定,这个案子最可能的判罚结果是什么?这个合同遭违约的概率有多大?某位特定的法官负责审理该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律师通常会根据他们的从业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预测。这些从业经验包括他们曾经处理过的案子、曾经谈判协商获得的结果、曾经代理过的诉讼等,然而,即使对经验丰富的律师而言,上述资源(经验)通常也是有限的。律商联讯伦敦办公室的律师兼法律自动化专家马克·史密斯告诉我们:“即使是经验极为丰富的律所合伙人,在面对特定案件时,可能也只有几十个相关的数据点。然而,有了自动化的数据系统,我们就可以把律所经办过的每一个相关案例都当作一个数据点,用更大规模的数据来分析手头的案件。”此外,自动化的电脑分析方法还可以避免人类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神经学偏差。专家声称,即使在目前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电脑已经能够以75%的准确率预测法庭的判决结果,而人工预测的准确性仅有59%。 [6] 随着这种大大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新技术的推出,所有律师事务所将别无选择地采用这些新技术——高科技的永动机从不会放过任何职业。律师曾经是聪明的、有野心的年轻人的首选工作之一,然而目前大家都相信,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出,法律行业的现状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显然,法学院的师生目前还没能很好地理解这一信息。史密斯告诉我说:“我曾在大学里给法学院的学生们授课,我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对这项科技创新知之甚少。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会建议我的孩子在未来从事法律工作。”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令人沮丧的建议恐怕会更频繁地传入我们的耳朵。虽然目前律师的失业问题似乎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悲剧。然而即使是最痛恨律师的人也不难看出,预测性算法这样的高科技绝不会仅仅出现在律师行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他行业的各种工作同样会受到这些科技的威胁。为了确保自己不从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上跌落下去,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寻求各种削减开支的方法和渠道,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能帮助公司削减开支的自动化过程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方便。如今,电脑技术已经可以自动驾驶车辆,并为大型飞机的起降自动导航。电脑算法可以分析X光片;批改大学论文;编写体育报道;在新闻和社交媒体的海洋中自动捕获各种对市场行情有影响的数据,然后据此精密地设置股票交易的时间点,从这些数据中获利。电脑科技已经创造出了一批“无灯化”的工厂——这些工厂不需要照明,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在里面工作。随着电脑计算能力的指数级上升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随着大数据技术将整个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推入全新的领域,自动化会越来越多地代替人们的劳动,上面的例子只是未来各种自动化革命的冰山一角。
然而,我们似乎并不应该为此感到担忧。作为一个教育程度高、技术能力强的后物质主义社会的成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理解:从理论上看,即使那些最耸人听闻的创新发明及其带来的效率提升都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点在过去是完全成立的。技术创新一直是一个利好因素,对就业市场而言更是一个利好因素。新技术可以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因此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一点效率提高(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更注重细节的管理策略等)虽然一开始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资源错配问题,但最终必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为我们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自工业革命以来,创新、效率和就业机会一直呈现一种铁三角关系。
然而,随着我们的整个经济被金融化的、追求高速回报的商业模式所主宰,如今我们的上述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进一步的创新和效率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做出乐观的回答。资本回报率是冲动的社会最大的经济目标。然而,随着商业公司以越来越高的效率用资本创造出更多的资本,大多数员工获得的回报却无法继续高速增长。在本书中,我已经多次提到关于美国劳动者收入的统计数据,现在我们不妨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数据的现实意义。虽然在经济增长率、公司利润和股价增值(特别是技术股票的股价增值)方面,美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然而我们这个巨大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效率超高的经济体却未能产生足够多的新就业机会,来填补经济危机中损失的就业岗位。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对美国未来就业岗位的预测,由于美国的就业岗位增长非常缓慢,经济学家预测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总就业人数都无法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事实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大型经济危机之后,就业岗位数目的恢复至少需要花12年的时间。 [7] 更重要的是,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远不如10年前的就业机会那么亲民。在后工业化世界中,大部分新就业机会要么是要求特殊知识技能的高端就业机会,要么就是大量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比如咖啡师和酒吧招待)。中等技术、中等工资收入的工作岗位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存在的基石,而目前这类工作机会却已经严重减少。这也是美国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和15年前相比下降7%的部分原因。 [8] 如今,报章杂志只要提到中产阶级,通常都会伴有“走下坡路的”“被掏空的”等修饰语。
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正在走向衰亡?虽然这一现象背后有很多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冲动的社会中的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变化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公司可以通过自动化大幅削减开支,同时缩小公司规模或者将多家公司合并经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等收入工作市场的萎缩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这样的现象背后还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现象: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技术革新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经瓦解甚至断裂。简言之,虽然技术创新仍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然而这些财富的更大部分流向了极少数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某些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被完全排除在财富的分配之外。在如今赢家通吃 [9] 的商业社会中,我们可以从少数赢家身上清楚地看到上述状况,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公司通过数据技术和规模效应的优势大幅提高经营效率,在这些公司进入的几乎所有市场中,本地的小型经销商都受到了碾压式冲击。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小群银行家通过金融工程的工具从房地产泡沫中获取了巨额“经济租金”,却把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纳税人。当然,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看到同样的情况:随着各种商业公司大规模采用自动化过程来削减开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这些创新实质上把公司利润的更大部分从员工手中转移到了管理层手中。
在冲动的社会中,创新的意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冷酷。这些科技创新虽然催生了更高的效率,却也使一小部分公司精英获得了利润蛋糕的更大份额——精英阶层获取的份额过于巨大,在大部分人看来早已超出了合理的水平,也无法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提供正面的影响。效率本身似乎也受到了污染:我们提高产出和降低成本的目标曾经是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总体进步程度,如今,提高效率似乎主要是为了给工厂、机器以及其他资产所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似乎抛弃了我们在20世纪取得的很多社会进步成果,而退回了镀金时代的浮华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我认为,这种社会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全社会更广泛的重视。这不仅关乎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且关乎很多社会上层人士(比如律师、股票交易员,甚至某些政客)的利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正视这样的问题,不仅需要问自己高效率创新究竟带领这个社会走向何方,还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创新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为了谁。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正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科技创新为社会带来普遍财富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世纪之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数千万欧洲和美国农民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当时这些受伤害的农民显然不会把工业革命当作正面的进步。然而,当时这些农民无法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令人讨厌的技术革新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工作机会。新技术虽然使农业部门的就业规模大幅缩减,却同时创造了很多全新的就业板块,比如铁路、大规模生产、公路建造以及公共事业等。这些新的板块不仅能为就业者提供更高的工资,还能为劳动者提供全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制造汽车不仅需要钢铁工人和轮胎工人,还需要工程师、设计师、市场营销专家,甚至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师,而这些新工作的收入又可以进一步创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现象称为“创造性的破坏风暴”,熊彼特认为,这种破坏的力量正是塑造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力量,它“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秩序,同时不断创造新的经济秩序”。总体而言,新的经济秩序总是优于旧的经济秩序。在大部分工业化社会中,创新所产生的生产力提高带来财富的广泛增加。我们的工资提高了,物价却降低了,同时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比如飞机引擎、X光照相技术、彩色电视机等)不仅创造了更多经济增长渠道和就业机会,还显著提高了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水平。当我们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我们的祖父母辈谈论美国战后繁荣时期的光辉过往时,他们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才对那个时代分外怀念:美国的战后几十年确实是一个全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美国社会就像一台创造财富的机器一般不停地运转着。
那么,这台财富机器现在怎么了?为什么这种旧式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如前所述,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创新活动不再具有足够的破坏性,至少缺乏熊彼特所描述的那种破坏性。亨利·福特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因为那场工业革命包括多个方面的突破:不仅是汽车生产技术及生产线的发明,还伴随着物流、商业管理、会计、石油化学、制药、通信等其他方方面面的革命。这些变革和创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共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秩序,这些创新的总和远远大于每一部分的简单加总。然而,我们今天的技术变革却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脑技术的提高虽然在个人权力领域带来了各种变革性的提高,然而作为一种工业的催化剂,电脑技术的影响通常只是让现存的工业过程变得效率更高——比如让生产线运转得更快,让同一家商店可以售卖更多种类的商品,或者让消费者能更轻松地与商家进行交流并消费。这些提高虽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却不足以点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火花。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创新水平不足。我们之所以难以取得划时代意义的突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间点:今天,要做出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创新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困难,因为那些比较容易的革新早就进行过了。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大幅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当时存在着许多巨大而明显的低效率元素,通过消除这些元素,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大幅提高生产率。比如,用机器取代动物完成农耕活动,用合成肥料代替粪便肥料。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那些挂在较低树枝上的水果”早已被我们摘下吃掉了,因此,今天要取得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创新成果,确实比过去更难,成本也更高。
一方面,创新确实变得比过去更困难了。另一方面,在冲动的社会所催生的金融化的商业模式之下,我们追求创新的动力也变得更弱了。如前所述,由于公司狂热地缩减开支,并尽一切努力保护季度盈利水平达到目标,研发开支被显著压缩了。而随着每家公司或多或少地削减研发开支,整个经济的科研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业界用于研发的投资每年增长7%,如今,研发投入的年增长率只有1.1%。 [10] 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公司愿意投资于科技研发,研发的目标也越来越多地与短期回报挂钩,愿意投资长期科研项目的公司越来越少。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曾经愿意大量投资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因此而闻名于世。当时的美国公司愿意首先取得创新性的科学发现,然后再慢慢研究如何将其转化为可以商业化的新技术。然而,如今美国的研发投资大部分不是用于“研究”,而是用于“发展”——将已经存在的技术转化为一系列新的产品和应用。这样的发展过程虽然也很有用,却无法真正产生突破性的科技成果。
在消费者产品的世界中,商家对微创新的追求已经为我们所熟知,微软公司通过将已有的技术转化为一系列改进不大的升级版而赚取了大量利润。这些升级补丁发布的时间点经过精心的设计,因此能为微软公司提供稳健的季度利润并促进股价的提升。但是,在经济的结构层面上,微创新现象甚至更普遍和更明显。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大部分创新的目标是把基础的商业流程(比如生产制造和物流)变得更加高效。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将生产线全面自动化,将发放银行贷款的过程流程化,将联系美国零售商和亚洲生产商的供应链数字化。这些效率方面的创新使消费者能享受到更低的商品价格。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创新也同时影响了这些消费者曾经拥有的工作机会。比如,沃尔玛在存货数据利用方面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沃尔玛甚至为此发射了自己的通信卫星),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不仅让沃尔玛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也使沃尔玛在与供应商的协商中获得了更多的谈判权。因此,很多沃尔玛的供应商不得不加速它们自身的成本压缩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意味着自动化和离岸化。在整个工业化经济中,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过程方面的创新导致整条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都必须努力压低成本,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制造业的规模一直在缓慢地萎缩,如今几乎进入了自由落体模式。1998—2004年,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工作消失了1/4;在日本,这一时期有1/5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在美国,2000—2007年,全国总计减少了6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占制造业工作岗位的1/3。 [11]
当然,我们不该把制造业的工作过于浪漫化和理想化。必须承认,这些生产制造工作常常是单调的、危险的,而且令人不快。很多工厂的工人非常愿意从这种简单的劳动中解脱,升级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去。制造业的自动化和离岸化趋势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它们只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风暴的表现形式而已:在理想的情况下,通过破坏工业化经济中旧的工作机会,自动化和离岸化的过程应该为下一代更好的工作机会创造空间,让这些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发挥更大的生产率,获得更高的工资,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在我们冲动的社会中,这些美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大部分失业工人无法在职业阶梯上更进一步,正因如此,战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广泛提高的时代已无法继续保持。事实上,很多工人失业后再次找到的工作仍然是同样简单的、重复的、危险的工作,甚至有些人的新工作还不如旧工作。
在此,我必须再次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很多方面看,西方世界的工人未能快速获得新的生产技能和知识,因此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而上述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没有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电脑化,现在的劳动者必须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认为,目前技术革新的方向是“技能偏好”的,即不断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新技能,由于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匹配,每年能够从这种技术革新中获得好处(甚至仅仅是能够跟上技术革新的脚步而不被抛弃)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小。虽然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显然非常必要(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股东革命以后被金融化动机主导的商业界,公司本身也显著降低了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力度。AT&T、IBM、通用汽车等公司都曾向员工提供长期、集中的训练课程,然而随着公司不断压缩人力成本,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显著减少了。很多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已被关闭,人力资源部门被外包,因此员工及其上级只能自行安排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事宜。事实上,现在的公司不仅希望员工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职业发展,还希望员工能够不断对自己进行再投资,从而使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最大化。在现在的公司文化中,公司已经不再认为雇主有义务帮助员工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再投资。IBM的资深员工考特·马丁在离开该公司后曾这样告诉《华盛顿时报》的记者:“IBM的员工不断轮岗。你必须不断掌握新的技能,并用这些技能包装自己,才能避免被裁员。当音乐停止时,你不希望自己是那个没有抢到板凳的人。” [12]
更糟糕的是,在这种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以优化程序为导向的创新潮流中,很多时候不断对自己进行再投资的员工也无法在职业阶梯上更进一步,因为那些曾经被他们当作职业目标的高级工作本身也在创新的过程中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速数据网络的出现,公司不仅能够将生产制造性质的工作离岸外包,甚至可以将许多知识技术性质的工作离岸外包。不管是会计记账、客户服务,还是工程设计、金融分析,甚至是建筑设计, [13] 这些工作都可以被外包至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俄罗斯、波兰或中国,而外包后的人力成本仅为原来的1/10。 [14] 即使在西方公司占绝对优势的领域,如软件研发、芯片设计、航空工程等,工作岗位也被大量离岸外包,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行业的竞争优势而享受稳定、有保障的就业环境。这些领域的创新使公司能够快速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和股价,如果仅靠传统的方法,这一成本压缩和利润提高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CEO们热情地拥抱了这些创新成果,就像他们的前任拥抱大型生产线、电话和其他传统科技创新成果一样。
在冲动的社会中,创新带来的真正危机是深层次的:创新曾经是一种提高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工具,创新的受益对象包括公司和员工,也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而今,创新的受益范围变窄了。创新越来越多地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效率,为资本提供高速的回报,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工厂生产的自动化,工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位产业工人每小时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因而能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对很多工作进行离岸外包的创新却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厂工人的生产效率显著低于美国工厂的工人,而美国公司却将各种工作外包到中国,中国企业则通过雇用更多工人来解决生产效率不足的问题。 [15] 将知识技术性的工作离岸外包同样会产生很多隐性的低效率问题。最近,我采访了一位曾负责管理亚洲离岸IT(信息技术)团队的管理人员,他这样告诉我:“离岸外包策略被当成一种非常新颖迷人的产品推销给美国的公司管理人员。这种策略被宣传得天花乱坠,大家相信离岸外包就是把美国的IT工作扔到墙的另一边。在那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工程师同样能帮我们高效地完成任务,而且每小时只收5美元,而美国的工程师则需要我们支付每小时50美元的工资。于是每位管理人员都会觉得:哇,这真是太棒了!然而,离岸外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只是轻松地把工作扔到墙的另一边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在工程领域,负责研发产品的团队以及产品的服务对象——公司管理人员——之间永远需要密切的互动和合作。如果这两组人员在同一栋大楼中工作,并且每天都能见面,能在门厅里进行非正式的交谈,那么这种互动会容易得多。然而,当你与为你提供服务的对象之间存在12小时的时差时,这种互动是很难高效进行的。” [16]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为降低成本而分割了整个工作环境,这种分割必然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然而,由于整体成本大幅下降,离岸外包策略仍然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至少对公司管理人员和投资者而言,这种策略确实提高了效率,为他们创造了财富。
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普遍持有这样的传统观点:全球化进程完全改变了商业世界的规则,当国外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1/10时,美国的公司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外界压力。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同样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对比欧洲和美国的反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确实存在更好的方法来管理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冲击。在欧洲,由于工会的影响更大,劳工管理方面的要求更严格,而且由于公司文化的不同,大部分欧洲公司继续在员工培训和再培训方面大量投资。在很多欧盟国家,由于工作机会被永久性离岸外包而失业的员工可以获得适当的培训,从而掌握新工作所需的技能。 [17] 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认为:“并不是说德国人或者瑞典人从不将工作外包,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司拥有更好的管理结构,它们可以把离岸外包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的母国,因此它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18]
然而,要获得更好的结果,首先要进行更多的投资。在自动化和离岸化的创新浪潮中,要保护公司的员工不受这些冲击的伤害,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公司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成本和支出。与此相反,我们的商业策略只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把全球化的成本(或者其他创新带来的成本)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手段完全转嫁给劳动者。然而,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并不是美国的传统。在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收缩,但工资的降低只占整体财富损失的1/3左右;其余的损失则被公司内部吸收——公司吸受损失的途径包括削减产量和降低对投资者的回报率。换句话说,在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公司为了降低劳动者所受的损失确实做出了严肃的努力,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方与劳动者共同分担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然而,随着股东革命的成功,新的技术使公司管理者能够更精确地设定成本缩减目标,同时工会也逐渐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上述损失分担的策略发生了改变。根据德勤咨询公司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在1981年的经济危机中,整体经济产出缩减,劳动者承担了1/2的损失;而在1990年的经济危机中,劳动者则吸收了3/4的总体损失。在每次经济危机中,成本压缩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投资者所攫取,而劳动者被迫吸收了大部分损失。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中(分别发生于2001年和2007年),劳动者吸收了98%的总体损失。德勤公司的上述研究报告这样写道:“在经济危机中,公司曾经是员工的保护伞,通过率先承担损失来保护员工的利益。然而,在如今全球化、高度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公司却越来越多地通过牺牲员工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润。” [19]
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离岸外包策略大幅削减了生产成本 [20] ,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中,公司利润和股价都在危机结束后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但是,过去20年来的离岸外包趋势导致这两次危机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就业机会不增加”的反常现象。冲动的社会的创新模式中存在一种本质性的不合理之处: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来增加利润,同时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曾声称,高工资是充满活力的消费者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提高工人工资,这些劳动者才可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商品。 [21] 亨利·福特说:“我们所生产商品的最主要消费者正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这是我们创造财富的秘密。” [22] 然而,到了20世纪末,亨利·福特的观点已经被商业界彻底抛弃。公司希望拥有钱包丰满的消费者(即使消费者本人无力支付这些消费支出,只要其他人愿意埋单就可以了)。然而,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消费者拥有了更强的个人能力,可以脱离整个社会的控制而独立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此同时,公司也同样利用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将公司的财富和员工的财富相分离。在战后的美国,商业界曾有相当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价值观,而如今这些东西已基本灰飞烟灭。从某个时刻开始,美国的商业界已经完全把效率创新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当作追求狭隘个人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家赫布·斯坦这样说道:“如果某件事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它必然会停止。”虽然赫布·斯坦这句话是针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说的,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美国今天的创新模式。或迟或早,市场总有一天会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修正。比如,不愿意在真正的科研创新方面进行投资的公司迟早有一天会没有新产品可供出售,苛待员工的公司迟早有一天会看到员工的绩效下滑,过度依赖廉价国外劳动力的公司最终会面临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事实上,在本次经济危机的余波中,有些公司已经表现出了对其之前所选道路的不满。离岸外包策略的奇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耀眼的光环。在产品质量和沟通交流方面,已经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很多国外的劳动者开始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有些西方公司已经逐渐将某些外包到国外的工作岗位重新移回国内——这种趋势被称为“回港”。随着回港趋势的兴起,公众对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展开了各种热烈的讨论。
与此同时,由于劳动者的技能和工作岗位要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持续,美国的教育部门面临很大的压力,对教育部门的改革和再投资势在必行。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最近几年,哈佛大学和MIT(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纷纷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全新教育项目,其核心是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集合了视频授课、在线互动、自动化等一系列先进的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知名大学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手段大规模生产高等教育资源,从而让普通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方便的渠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熏陶。MOOC的模式目前已经走出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扩展。很多支持这项改革的人认为,这种网上课程模式仅仅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教育革命的开端。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整个高等教育过程(从招生入学到课程选择,再到学习和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都可以数量化,因此高等教育过程应该能够获得根本性的提高。借助大数据,教授、学生、辅导员和家长都能以过硬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哪种教学模式(或者哪种教材、哪种住宿模式、哪些课外活动)能让学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所学内容。2013年,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加里·金在接受《纽约客》记者内森·赫勒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可以把一切进行量化:每一个学生,每一间教室,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房屋,每一项课外活动,每一位保安,所有东西。我们可以搜集一切信息,并将其汇总于此,然后让这些信息为学生所用。” [23]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改革激起了人们多大的热情。支持这些改革的人认为,如果这样的教育革命真的发生,必然会对就业情况和社会总体财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项改革的影响可能超过过去200年的所有革新措施,因为这样的教育革命能让美国回归一种进步的、以未来为目标的创新模式。也许在创新之树上,那些挂在较低树枝上的水果确实已经被采摘完毕。但如果教育系统的升级能够培养出更多掌握最新技术的毕业生,如果公司和政府愿意提高它们在战略部门的投资(如能源和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就完全有希望看到更多突破性的科研创新成果。这种突破性的成果完全可能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产业和全新的工作类别。
比如,如果我们能够研发出一种全新的能源技术(不产生碳排放,经济上可行,并且具有去中心化特点的能源技术),就完全可能为我们的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同样,在生物技术领域,虽然最近几十年来该领域一直未能兑现对公众的承诺,但这一领域同样具有产生突破性成果的潜质。生物技术领域的突破同样可以创造出一些全新的经济部门。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指出,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可能很快就能“种植”出替代器官,并且可以对这些器官进行商业化生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买到工厂生产的皮肤,实验室已经可以种植出能用于移植的简单器官,比如气管。曼德尔认为,一旦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覆盖更多、更复杂的器官,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巨大产业。这个产业会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分销系统、自己的出口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其中不少工作机会可以提供很高的工资——比如我们需要进行器官质量控制的技术人员。曼德尔告诉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创新的曙光,我们知道这些创新的成果马上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们可以轻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如果你让我猜的话,我认为10年后我们将会面临劳动力短缺而非工作机会短缺的问题。” [24] 对曼德尔及其他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而言,我们的创新机器和工作创造机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突破性成果,是因为今天复杂的技术挑战、不必要的政府监管等负面因素推迟了成果的出现,而现在,我们很快将迎来划时代的突破性创新成果。
然而,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的创新机器和工作制造机器显然出了不小的毛病,如果不对我们的冲动型创新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变,即使回港策略和生物技术革命等正面因素也难以帮我们力挽狂潮。凯恩斯曾这样说过:“市场可以长期保持非理性的状态,在市场对这种非理性进行修正之前,也许我们早已破产了。”我们冲动的经济已经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这些发展随时可能先发制人,在我们做出调整之前就对我们短视的创新策略进行冷酷无情的修正。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就是今天有许多大型技术公司利用金融工程来有效回避市场的修正性约束。以微软为例,与很多成熟的技术公司一样,微软通过早期的技术突破(尤其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发明)获得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以此不断赚取大量现金。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理性的商业策略应该是将这些现金的一大部分再投资于下一代科技研发工作。然而,拉佐尼克指出,虽然微软每年确实在研发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但由于公司未能成功地投资于能使公司运营效率提高的领域,公司员工根本无法高效利用这笔研发投资。事实上,那些本该用于升级经营功能的投资被用来回购本公司股票:2003—2012年,微软总共花费了1 140亿美元来回购本公司股票,这笔支出大约是微软科研支出的1.5倍。这些举措导致了典型的冲动的社会。过去这些年来,微软通过不断推出各种效果平庸、充满漏洞的系统升级版本,来吃Windows操作系统的老本,而研发全新技术和全新产品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即便如此,微软仍然成功地通过大规模的股票回购策略达到了保持高股价和安抚投资者的效果——通过这样的金融手段,微软成功规避了效率市场本应给予它的惩罚。拉佐尼克认为,微软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让员工充分参与经营活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公司的高股价”。 [25]
微软这种短视的、高度金融化的创新策略已经成了美国商业文化的流行病。许多大型美国技术公司都发现,在科技研发的投资和回报方面,与其投资新的科研项目,不如吃过去研究成果的老本,因为后者能够提供更高效的资本回报。因此,这些公司大量削减为未来创新做准备的组织能力方面的投资(比如对员工的技能培训),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在这方面,IT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IBM、惠普、施乐等公司几十年来对科研的大量投资(以及大量公共科研投资),互联网技术不可能那么早就以如此惊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26] 然而,正是这个曾经创造过奇迹和辉煌的行业,如今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很多公司却宁愿用科技研发的资金回购本公司股票。拉佐尼克告诉我,2003—2012年,微处理器的发明者英特尔公司在回购本公司股票上花费了597亿美元,这项支出仅比科技研发支出低几十亿美元。网间结构技术重要的早期奠基者思科公司则在回购本公司股票上花费了750亿美元,超过了其科研预算的1.5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商业界的创新机器确实已经出了大问题:创新的目的不再是创造新的产品和技术,也不再是为经济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是用各种方法来补偿新发明和新价值的匮乏。
拉佐尼克认为,问题的关键正是股东革命的核心理念,即股东必须对公司的所有表现(包括公司的创新)负责,因此,股东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然而,实际上除了通过筹集初始资本和发售新股这两种方式为新项目融资外,股东根本不会真正参与公司的创新过程。拉佐尼克认为:“事实上,公司的利润是由公司的劳动者创造的,跟股东根本没什么关系。” [27]
从现实的角度看,工业界不愿意在员工身上投资的现象反映的是对劳动力普遍的冷漠态度。如果这种冷漠出现在30年前,很可能早已导致了一次市场修正。确实,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公司敢像今天这样冷酷无情地、像对待消耗品一样对待自己的员工,恐怕早已遭到劳动者的强烈反抗。然而,正像今天的管理者可以使用金融工程的工具来逃避市场的修正以免于惩罚一样,今天的管理者也学会了逃避劳动力市场的反抗。经历了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无情裁员、离岸外包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结构重组”,美国的劳动者似乎已经放弃了反抗。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罢工及其他形式的劳工活动频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参与人数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会为了保住工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愿意向公司妥协。几年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汽车制造商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汽车制造商支付给新工人的薪酬仅相当于老工人薪酬的一半。 [28] 2013年,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威胁公司的机械师们,如果他们不接受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削减,波音就将整个公司搬去没有工会组织的南卡罗来纳州。 [29] 这次劳资斗争以资方的胜利告终,波音公司的股价随之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显然,随着每一轮的工资和福利削减,随着每一次经济危机后不增加就业岗位的复苏过程,劳动者的谈判筹码变得越来越少。经济学家赫希·卡斯珀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失业的时间越长,就越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他们只求能回归工作岗位就行——公司的管理人员当然很乐意利用这种自我反馈的心理模式。 [30] 一些后续的研究显示,失业时间每增加一年,所谓的“保留工资”就会下降3%~7%。这一心理现象和其他原因共同作用,导致失业工人重新找到新工作时,平均收入比原工作的工资低20%。 [31] 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不难理解长期失业的新现实,以及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恐惧心态。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相信,公司管理人员可以随意对待公司员工,把员工当作吸收成本的工具,以追求越来越高的效率——虽然这样的商业策略会造成高昂的社会成本。200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显然有很多西方公司以经济危机为借口,抓住机会压低员工工资,大幅裁员,并加速离岸外包进程。更重要的是,虽然美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工作岗位和薪酬的削减仍在继续,公司管理人员对待员工的态度展现了空前的恶毒和傲慢,似乎公司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地位拥有绝对的自信,完全不担心员工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到了21世纪初,许多离岸外包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冷酷和算计:比如,曾有公司以取消离职补偿金为威胁,胁迫因离岸外包而即将失去工作的员工在工作的最后几周内培训抢走他们工作的外国员工。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种冷酷无情的策略严重打击了公司员工的士气,也因此伤害了公司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公司的管理者却选择继续采取这些措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公司还广泛强调团队意识,并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更人性化的公司文化。回想当初,再对比今天的情况,我们不禁感到一种苦涩的讽刺意味。突然之间,美国的商业界再也没有团队,也没有人情。一位IT公司的前高管告诉我:“公司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向员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保持机构精简,我们必须保持对员工的吝啬,这意味着我们会把所有可能外包的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即使这样做会严重伤害公司,会彻底摧毁员工的士气,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做。然而,他们似乎忘了过去10年间他们一直在说:‘哦,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好的资源!’——在知识型产业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现在我们却要为了缩减开支和保护季度奖金而破坏这种良好的传统?”
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市场对过度的劳工运动的一种修正罢了,在劳工运动最为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公司管理层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而那时的工会也不曾对管理层抱什么同情。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修正的程度也未免太过分了。人们曾经普遍相信员工的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是紧密关联的,我们相信工作是一种靠集体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相信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和管理层应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然而,这些理念如今都已走向终结。工会组织曾在美国普遍存在,工人可以在这些组织的帮助下联合起来,与雇主协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环境。然而,如今美国的工会组织已经严重衰退,这是上述信念的衰亡带给劳动者的巨大损失。然而更大的损失是职场已不再具有社区的性质。在美国,职场曾经是一种社区化的空间,职场上的劳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半永久性的。在这个社区中,有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有同事间的友谊和上级对下级的关怀和指导。职场社区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与私人生活相关的社区。然而,在冲动的社会的效率市场中,职场社区已被慢慢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立的、非人性化的、高效率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安全和永久的,也没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所有温情都被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所取代。
当冲动的社会进化到这一步,传统的生产者经济终于彻底死亡。在传统的生产者经济中,劳动者为他们的生产者身份而骄傲,劳动为每一位工作者带来快乐,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也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认知。然而从这一时刻开始,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所说的,一个典型的劳动者需要不断与工作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做斗争,因此劳动者已变得越来越像消费者,他们“不断渴望着新的东西,将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的旧物无情地丢弃,他们完全不像这些东西的所有者,因为所有者总是会极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东西”。 [32] 换句话说,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劳动者曾将自己视为稳定社区的一部分,并把自己的所有同事都视为这个社区中的邻居。然而,如今的劳动者更多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人,他们学会了如何轻松地建立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学会了如何快速地抛弃过去,他们将所有事情都视为暂时的,把个人的生存当作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最高目标。不难看出,在这种新的职场环境中,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恋主义倾向,而这些情绪早已感染了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中,我们很难相信美国的工业复兴能够顺利地发生。
我认为在目前冲动的社会中,存在更多根本性的原因,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事实上,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很多投资恰恰是为了阻止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使回港运动真的能够继续下去,回港的工作数量也远远低于被外包的工作数量。这是因为,在离岸外包潮流兴起之后的2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自动化技术始终在不断地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消费品生产公司已经在研发封闭型的、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需要任何工人操作,只有监管和修理的功能还需要人类来完成。能够完成工业生产任务的机器人不仅功能变得更加先进和复杂,成本也在不断降低。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人类劳动成本相比,工厂机器人的价格下降幅度达到了50%。即使在劳动力相对充足的中国,也有一些工厂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者。而在发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如日本)中,无人工厂早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景。早在十几年前,日本的机器人生产厂家FANUC就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了。这些机器人的生产效率很高,每24小时能生产50个机器人。FANUC的工厂可以在完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连续运行几天,如果不是因为必须停工以使物流方运走已经造好的机器人,FANUC的工厂甚至可以全自动运行更长时间。 [33]
与此同时,美国的机器人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每当新的机器人技术被投放市场时,公司总能迅速将这些新技术运用到自己的生产活动中。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器人模型,名为巴克斯特。巴克斯特是被专门设计来完成流水线工作的。每一台巴克斯特售价约22 000美元,这个价格低于美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使用者可以轻松地对巴克斯特进行编程,然后生产线工人就能“教”这些机器人如何完成生产工作。 [34] 布鲁克斯设计巴克斯特的本意是希望这种机器人能协助人类完成生产线工作,然而布鲁克斯告诉我,有些公司认为巴克斯特不仅能成为人类的助手,甚至可能全面取代人类的劳动。最近,在波士顿举行过一次关于机器人技术的专题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布鲁克斯提到,某些公司将巴克斯特视为一种既能帮助工厂增加产量,又不会产生额外管理成本的优秀工具;有了巴克斯特的帮助,工厂就不需要为了增加产量而雇用更多低工资的工人了。“很多向我们咨询的小公司都表示,它们可以通过竞价获得更多的工作合同,但它们不愿意雇用夜班工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些夜班工人晚间长期待在工厂里。因此,这些公司希望能够使用巴克斯特来完成夜班的流水线作业。有了巴克斯特,这些小公司就不用再雇用更多的工人,于是它们会有更强的竞争力,也能赢得更多的合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工厂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工人。” [35] 在冲动的社会中,制造业未来的工作岗位将不再是所谓的蓝领岗位,而会变成无领岗位。
被机器人逐渐取代的工作远不止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岗位。如前所述,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脑可以完成各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创造性的工作,甚至连律师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今天,我们读到的很多体育简报完全是由电脑算法编写的。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脑将很快胜任更多与概率相关的分析工作,而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却需要苦读数年才能掌握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当然,仍然有很多专业技术岗位只有人类才能胜任,但是这些岗位的工作要求将会与现在非常不同。上文提到过的在伦敦担任律师的高级自动化专家马克·史密斯告诉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法律行业将被分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第一个部门由少数能力很强、工资很高的超级律师组成,他们拥有过人的才智、出众的管理技能以及高超的社交能力,雇主仍然需要依靠他们来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至少在目前看来,电脑在短期内不可能具备上述高级能力与技巧。第二个部门则包含大量能够以沃尔玛模式大规模处理的简单工作,我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自动处理成千上万的简单案件,如无争议的离婚案件或者住房抵押贷款合同纠纷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整个劳动力市场都会和律师行业一样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再见,平庸时代》中更具体地描绘了这种情形。在考恩对未来的预测中,所有劳动者中能力最强的前15%将会成为生产力超高的“超级劳动者”,他们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或者知道如何管理其他的超级生产力要素。因此,对这些超级劳动者而言,每一代新技术的推出都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技术的发展能帮助这些超级劳动者获得利润的更大份额。超级劳动者之下的第二阶层是少数“服务提供者”,包括按摩师、健身教练、室内装修师、个人助手、课程辅导员、艺术家以及娱乐业人士,这些人通过向超级劳动者提供服务,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在服务提供者这个阶层之下,情况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系统地消除了所有能够自动化或者可以被离岸外包的工作岗位,因此对其余的劳动者而言,可供选择的工作非常有限。他们只能从事低技术的服务类工作,比如食品服务人员、保安、清洁工、负责维护草坪和花园的园丁、美容美发师以及家庭健康服务者等。从乐观的一面看,这类工作由于很难完全自动化或外包,因此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考恩的《再见,平庸时代》一书引用了MIT的劳动力市场专家戴维·奥特尔的研究成果。戴维·奥特尔认为,这类低技术的服务工作“通常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并提供手工服务,因此相对难以取代”。然而从悲观的一面看,奥特尔认为,这类工作永远只能是一些低工资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术非常简单,任何人只要学上几天都可以从事这些工作”。 [36]
事实上,这些低技术工作的缺点远比优点要多。比如,大数据技术使雇主可以随时方便准确地监控工人的生产率,因此工人必然时刻承受必须达到某种业绩指标的压力。管理者也会不断对工人进行评分和考核,就像今天网友会对餐馆和各种线上商品进行评价一样。公司会试图监控所有可能影响业绩表现的因素。因此,员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工作的申请过程到实际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会受到雇主越来越严密的监控和评估。考恩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时说:“如果你是一位工人,你身上将时时刻刻贴着一个信用分数一般的评分。 [37] 事实上,目前这种评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了。这个评分反映出你的很多信息:你有多可靠?你从事过多少种不同的工作?你是否曾经被他人起诉?你收到过多少张交通罚单?”考恩认为,未来会出现一种精确度量所有事物的趋势,而对劳动者的上述评估只是该趋势的一种体现。考恩说:“然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来说,长期受到监视和测评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不快。” [38] 这是市场与自我的融合所带来的阴暗面:劳动者像一件物品一样被研究、测评、分析,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必然会被磨去个性的棱角,成为商业机器中更高效的螺丝钉。(事实上,美国银行等公司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美国银行要求员工佩戴数字徽章,这种徽章可以随时自动监控员工的动作和互动情况,监控的对象甚至包括员工说话的语调,而这一切信息的搜集都是为了更好地测评员工的工作效率。 [39] )随着这种趋势的盛行,中下层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会变得更差。考恩认为,如果最上层的超级劳动者变得比今天更富裕,那么其余的大部分人必然会变得更贫穷。随着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中位数收入将显著下降,很多贫穷的人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为富裕阶层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抗拒增加税收的政策。考恩说:“政府不会通过高税收、低福利的方法来达到财政预算的平衡,而会让大部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这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低产阶级’。”
很多批评家认为考恩的上述观点过于悲观。然而,目前我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这种未来的影子。很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绩效考评算法来决定哪些员工将被裁员——如果所有公司都采用同一套算法,那么被裁员的人或许就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这种现象是科技创新的终极腐败:本应被用来帮助劳动者升级职业技能、提高工作稳定性的技术反而被雇主用来伤害劳动者。当然,大数据也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有益的影响。比如,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重塑我们的教育体系。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技术对社会结构的伤害日益严重,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全新的教育系统,甚至需要某种全新的经济部门来扭转这种负面趋势。本次经济危机之后,大量工作岗位的消失和失业者失业时间的延长造成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大量劳动者已经走上了一条缺乏希望的下坡路。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虽然能够获得中等水平的工资,职业技能却相对低下,因此制造业的崩溃产生了大量工作技能不足的失业工人。这些人以男性为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这些人很可能长期处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态。而这些失业人群会进一步导致不稳定的家庭状况,引发更多社会问题,比如下一代人的吸毒问题、青少年怀孕问题、辍学问题等。于是,这些人的下一代将更难逃离低收入阶层,更难获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数字技术将大幅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但中下阶层的孩子根本无法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这些好处。在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的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和地位却在不断提升。由于我们的经济对高级工作技能的需求越来越强,稳定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所带来的优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上层阶级的孩子不仅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更容易进入成功的社交圈,找到优秀的配偶,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当前这些令人担心的情况,即使想象力不怎么丰富的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考恩所描述的那个糟糕的世界确实正在降临。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因为某些大规模的灾难(比如另一场经济危机或者贸易战争)而变得更糟,而是因为数不清的科技升级,以及商业界为了进一步缩减开支、提高效率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考恩说:“我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个趋势停止。当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国家分裂为两个部分:能够获得科技进步的好处的人将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成功国度中,而其他所有人则会在一个苦难的国度里挣扎。” [40]
让我们感到分外矛盾的是,如果仅看很多传统的指标,上述一切根本不应该发生。美国经济正向着更高效的、生产率更高的方向增长,每年我们都在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GDP。华尔街和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欣欣向荣,这部分得益于各种科技公司的不断创立和发展。2013年,IPO(首次公开募股)的私有公司数量上升了40%, [41] 达到了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42] 当然,其中很多最大规模的IPO都出自技术公司,这一点恐怕我们都不难猜到。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创新中的绝大部分似乎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复兴。其中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年末上市的推特公司。作为一家社交媒体网站,推特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向公众表达自我的领先平台”。由于在推特上发送消息是如此简单和高效,我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已经患上了刷推特的强迫症。当中东的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我们在推特上发文庆祝;当我们见证某些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行为时,我们在推特上发文表达崇敬。甚至当我们堵在车流中,外出活动,或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也要发送相关的推特信息。推特平台创造了一条近乎永不停息的自我表达的河流(目前全世界每分钟总计发送347 000条推特信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推特信息,尤其是广告商通过实时搜集和分析我们的推特信息,可以将我们自我表达的行为转化为消费的动机。推特前CEO迪克·科斯特罗在向投资者宣讲时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很多失眠者会在深夜发送关于失眠的推特信息。科斯特罗解释道:当NyQuil(一家医药公司)的广告商侦测到这样的信息时,就可以向这些用户推送该公司的安眠药产品(这种药的名字叫作ZzzQuil)的优惠促销信息。科斯特罗向投资者这样保证:这类推特信息每天都会不停地在推特平台上出现,这些信息为广告商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与目标客户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接触”。推特的IPO获得了巨大成功。投资者们争先恐后地抢购该公司的股票,在新股发售当天收盘时,推特的市值已经达到310亿美元。然而,虽然推特成功策划了近年来最成功的IPO,该公司当时却尚未产生过任何利润。
我们不会因为它们在IPO中获得了巨大的金钱利益而仇视科斯特罗或者推特。然而,推特的成功以及公众对推特上市表现出的极端兴奋情绪却凸显了冲动的社会中科技创新与劳动力市场互动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那种能够稳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科技创新已经不能获得效率市场的表彰。如今我们追求的是像推特这样的快速成功。(推特的成功掀起了一波投机的浪潮,投资者可以迅速在这样的浪潮中收获利润,然而这场热闹的盛宴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就业机会。)这种创新反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并且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
帮助我们减少劳动需要的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于是现在的商业界更愿意投资于技术,而不愿意投资于劳动力。简言之,投资于机器人、服务器组群或者某种对语义敏感的算法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投资于员工筛选和培训的回报率。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指出,这种现象会迅速产生滚雪球效应。随着公司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减少劳动需要的科技研发,不仅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资本变得更少了,而且这些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或就业不足,从而导致整个劳动力群体争取工资的谈判力下降。由于科技提供的高回报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劳动力能吸引到的资本就相应变少了。于是,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利润和财富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小。在不久前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产出大约有41%流进了劳动者的口袋(劳动者获得回报的形式包括工资、养老金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其余的部分则由投资者获得,或者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获得。然而到了2007年,在美国的总体经济产出中,劳动者获得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31%。虽然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工会组织权力的下降,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动化和外包化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使公司可以在完全不提高劳动者工资(事实上,劳动者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压低生产成本、降低售价、提高销售量,从而将更多的利润输送给投资者。 [43] 正如劳伦斯·萨默斯和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借助新技术,公司在提高工业产出的同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危机结束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率都出现了大幅提升,然而美国的中位数工资和中位数家庭收入却没有出现上升趋势。显然,生产率和效率提高带来的财富越来越多地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方向却十分明显。
在冲动的社会的影响下,美国越来越不像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像是贫富差距巨大的二流经济体。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仿佛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上。政治科学家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曾这样写道:“在一代人之前,美国的贫富差距虽然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却也是富裕民主国家(又称混合经济体)中的重要一员。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被整个社会共同分享。然而,到了1980年左右,这种美好的情况却一去不回。美国偏离了混合经济体的方向,而向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政府的方向高速前进。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政府的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呈现出很高的集中度。” [44] 这种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与冲动的社会的追求高度吻合,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趋势不会继续下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工会组织的衰落以及公众文化对效率市场理论的接受,美国的公司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公司管理层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操作余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我们知道任何群体一旦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就一定会积极使用这种权力。事实上,美国的公司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这种风气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权力的变化,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公司的管理者们自愿放弃利润蛋糕的一部分,将这部分利益发放给员工。公司管理者这样做是为了与劳动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同时,管理者这样做还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当劳动者的工资不断上升时,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购买更多消费者产品。然而,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我们的企业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长远眼光和宏观视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达尔文式的论调。如今的商业文化不断强调,为了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挑战(全球化、数字化、经济危机、沃尔玛的兴起)中生存下去,公司必须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然而,目前美国的公司利润已经占到国家经济总产出的11%,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这个比例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上述达尔文式的理由并不能为公司压榨劳动者的行为提供合理的依据。 [45] 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普林斯顿大学劳动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曾说:“公司利润占整体经济产出的比率几乎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因此所谓‘公司无力负担更高的劳动者工资’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46]
然而,虽然这种说法缺乏理论依据,美国社会文化却坚持继续宣扬这一论点。很多时候,这种论调会公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很多制造业公司宣称,只有降低员工工资才能保证公司在危机中继续生存下去。正是以这样的理由为基础,不少公司在危机中确实成功压低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虽然公司目前的利润水平已经大幅回升,然而绝大部分企业都拒绝将员工的工资回调至危机前的水平。比如,在经济危机结束之后,虽然卡特彼勒公司的利润已经创下了新纪录,公司却拒绝解除在经济危机中设置的工资增长冻结计划。愤怒的公司员工要求卡特彼勒公司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而公司时任CEO道格拉斯·欧博赫曼却声称,只有继续实施工资增长冻结计划,才可能保持卡特彼勒公司的竞争力。然而,自2010年至今,欧博赫曼自己的薪酬几乎翻了一番。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时,欧博赫曼告诉记者:“我总是向公司的员工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赚的钱永远都不够多,我们的利润永远都不够高。” [47]
在成本压缩方面,美国公司也表现得同样厚颜无耻。《华盛顿邮报》2013年年末的一则报道显示,虽然美国公司的利润和股东回报率几乎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商会却向其成员公司提供建议,教它们如何“利用社会福利措施(比如住房补贴和粮食补贴)来解决低收入员工的生活问题,因为通过这样的途径,公司能够以零成本解决员工周转率过高的商业问题。” [48]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应该无视这些经济腐败问题,应该任由道德的漏洞变得越来越大。反正拥有权力的人总能以更多的创新方式合法地占有利润蛋糕的更大份额。只要利润蛋糕可以越做越大,也许社会上的其他公众应该停止对道德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的担忧。然而,问题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不仅是美国社会的标志,也是美国社会的引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人能够保证利润蛋糕真的会不断变大。即使我们能够通过某些巧妙的方法避免贫富差距增大对社会稳定性造成大规模的影响(也许穷人每天都忙于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早餐图片,因此没有时间去抗议和革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因为自身的内在特征也绝不可能拥有长久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冲动的社会中,人们对更快、更狭隘的自我利益的不懈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的巨大创新能力被用来实现一些错误的目标。因此,技术公司会继续用大量现金回购本公司的股票,或者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技术专利权,然后对使用类似技术的竞争对手提起法律诉讼。与此同时,潜在的投资者(刚从学校毕业的聪明而富有野心的年轻人)会继续追捧能帮他们快速赚到现金的创新公司,虽然这些创新并不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员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曾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如果只需要设计出一个时髦的App,就能让谷歌公司通过人才收购的方式付给你2 000万美元,那又何必费力去发明下一台T型车呢?” [49] 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之所以迟迟未能产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性产品和理念,正是因为它们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浪费在了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因此科技产业只能不断吃现成技术的老本,而它们推出的新产品一代比一代弱。要想把整个经济的利润蛋糕真正做大,就必须在科技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性成果,然而科技产业的上述倾向导致这种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权力,我们可以轻松安全地获得很多短期的奖励,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早已失去了追求长远目标的动力。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市场应该察觉到人们的这种短视行为,并对其进行惩罚。然而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中,市场也早已成了这个骗局的帮凶。因此,当微软、苹果、英特尔等公司花费数百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时,股东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忧,反而为公司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例子:2013年8月,由公司“狙击手”转行为积极投资者的卡尔·伊坎宣布(当然是在推特上宣布)他已经收购了1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并要求苹果公司花1 500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卡尔·伊坎认为,这样的回购行为可以将苹果公司的股价从每股487美元抬升到每股625美元(也就是说,卡尔·伊坎可以从中获得2.8亿美元的净资本回报 [50] )。卡尔·伊坎的行为简直是冲动的社会的经典桥段:他既不懂电脑技术,也不精通经营结构,因此绝不可能为真正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形式的贡献。卡尔·伊坎只懂得如何利用金融技术把他手中巨大的资本蛋糕变得更大。很多更现实的观察者认为,苹果公司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回购本公司的股票,而应该用这笔钱重振公司的创新流程,或者至少应该用这笔钱去研发某种比苹果手机更有技术含量的新产品。然而,市场却对卡尔·伊坎的行为十分满意。对市场而言,与投资技术创新相比,用大笔现金回购本公司股票才是高效使用资本的正确途径。事实上,当天股市收盘时,苹果公司的股价上升了3.8%。卡尔·伊坎的一条推特就让苹果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00亿美元。
[1] Alex Aldridge, “Law Graduates Face a Bleak Future at the Bar,”The Guardian , Nov.25,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law/2011/nov/25/law-graduates-bleak-future-bar.
[2] Daniel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 — Or —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 62, no. 909 (2013): 965.
[3] Laura Manning, “65 Students Chasing Each Training Contract Vacancy,” Lawyer 2B,June 28, 2011, http://l2b.thelawyer.com/65-students-chasing-each-training-contract vacancy/1008370.article.
[4] John 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The New York Times , March 4,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3/05/science/05legal.html?pagewanted=1&_r=1&hp.
[5] Thor Olavsrud, “Big Data Analytics Lets Businesses Play Moneyball,” Computer worldUK, Aug. 24, 2012, http://www.computerworlduk.com/in-depth/it-business/3377 796/big-data-analytics-lets-businesses-play-money ball/.
[6] Daniel Martin,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 — Or —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 62, no. 909 (2013): 938.
[7] Gary Burtless, “How Far Are We From Full Employment?” Brookings, Aug. 27,2013.
[8] Paul Krugman, “Def ining Prosperity Down,”The New York Times , July 7,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08/opinion/krugman-def ining-prosperity-down.html?src=recg;“Median Household Income, by Year,” table, DaveManuel.com, http://www.davemanuel.com/median-household-income.php; Robert Pear, “Median Income Rises, but Is Still 6% below Level at Start of Recession in ’07,”The New York Times , Aug. 21, 2013,http:// www.nytimes.com/2013/08/22/us/politics/us-median-income-rises-but-is-still-6below-its-2007-peak.html; past years’ data was adjusted using the CPI Inf lation Calculator at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 http:// www.bls.gov/data/inf lation_calculator.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Winner Takes All... Sometimes,” review of Robert H.Frank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1995),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 1995), http://hbr.org/1995/11/the-winner-takes-allsometimes/ar/1.
[10] “The New Normal? Slower R&D Spend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Macroblog , Sept. 26, 2013, http://macroblog.typepad.com/macroblog/2013/09/the-new normal-slower-r-and-d-spending.html.
[11] Adam Davidson, “Making It in America,”The Atlantic , Dec. 20, 2011, http://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1/making-it-in-america/308844/.
[12] Patrice Hill, “The Mean Economy: IBM workers suffer culture change as jobs go globa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demand new skill sets, lower labor costs,”The Washington Times , August 26, 2012,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aug/26/innovators working-their-way-out-of-a-job/?page=all.
[13] Vinay Couto, Mahadeva Mani, Arie Y. Lewin, and Dr. Carine Peeters, “The Globaliz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 The Facts and Fallout of Next-Generation Offshoring,” Booz Allen Hamilton, https://offshoring.fuqua.duke.edu/pdfs/gowc_v4.pdf.
[14] Fareed Zakaria, “How Long Will America Lead the World?”Newsweek , June 11,2006,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6/06/11/how-long-will-america-lead-the world.html; and “Graphic: Going Abroad,”BloombergBusinessWeek , Feb. 2, 2003,http://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2003-02-02/graphic-going-abroad.
[15] Sam Ro, “The Case for the Robot Workforce,”Business Insider , December 4, 2012,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obot-density-for-select-countries-2012-11. Accessed February 1, 2014.
[16] Interview with author.
[17] Bruce Stokes, “Europe Faces Globalization – Part II: Denmark Invests in an Adaptable Workforce, Thus Reducing Fear of Change.” YaleGlobal, May 18, 2006,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europe-faces-globalization-%E2% 80%93-part-ii.
[1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 John Hagel et al., “The 2011 Shift Index: Measuring the Forces of Long- Term Change,”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pp. 10-11.
[20] Diana Farrell et al., “Offshoring: Is It a Win-Win Game?” McKinsey and Company:Insights and Publications, Aug. 2003,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employment_and_growth/offshoring_is_it_a_win-win_game.
[21] Hedrick Smith, “When Capitalists Cared,”The New York Times , Sept. 2,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9/03/opinion/henry-ford-when-capitalists-cared.html?_r=0.
[22] William McGaughey Jr., “Henry Ford’s Productivity Less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Dec. 22, 1982, http://www.csmonitor.com/1982/1222/122232.html.
[23] Nathan Heller, “Laptop U,” May 20, 2013
[24] Interview with author.
[25] Interview with author..
[26] Lazonick and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p. 31.
[2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anuary 10, 2014.
[28] “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The Economist , Jan. 19,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69570-growing-number-american-companies-are moving-their-manufacturing-back-united.
[29] 此外,南卡罗来纳州政府还向波音公司提供了约80亿美元的免税优惠。
[30] 当然,由于当时的美国经济非常繁荣,而且公司尚无法使用国外的劳动力,因此,工会仍然能通过各种努力和斗争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
[31] Alan B. 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lecture delivered at “Learning and Labor Economics” Conference at Oberlin College, April 26,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 iles/docs/oberlin_f inalrevised.pdf.
[32]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 pp. 4–5.
[33] Christopher Null and Brian Caulf ield, “Fade to Black: The 1980s Vision of‘Lights-Out’Manufacturing, Where Robots Do All the Work, Is a Dream No More,” CNNMoney,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business2/business2_archive/2003/06/01/343371/index.htm.
[34] “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
[35] “Robots Are Coming, Part 2,” SoundCloud discussion on InnovationHub, https://soundcloud.com/innovationhub/robots-are-coming-part-2.
[36] Interview with author.
[37] NPR Staff, “Tired of Inequality? One Economist Said It’ll Only Get Worse,” NPR.org,Sept. 12, 2013, http://www.npr.org/2013/09/12/221425582/tired-of-inequality-one economist-says-itll-only-get-worse.
[38] Ibid.
[39] Hannah Kuchler, “Data Pioneers Watching Us Work,”Financial Times , February 17,2014.
[40] NPR, “Tired of Inequality.”
[41] Paul Sullivan, “Twitter Tantalizes, but Beware the I.P.O.”The New York Times , Oct. 25,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26/your-money/asset-allocation/twitter-tanta-lizes-but-beware-the-ipo.html?hpw.
[42] “IPO Performance,” graph, Renaissance Capital IPO Center, http://www.renaissanc ecapital.com/ipohome/press/mediaroom.aspx?market=us.
[43] Susan Fleck, John Glasser, and Shawn Sprague,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Monthly Labor Review (Jan. 2011).
[44]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11), pp. 3-4.
[45] “Graph: Corporate Prof its after Tax (without IVA and CCAdj) (C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conomic Research,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graph/?g=cSh.
[46] 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47] Mina Kimes, “Caterpillar’s Doug Oberhelman: Manufacturing’s Mouthpiece,”BloombergBusinessWeek, May 16, 2013,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5-16/caterpillars-doug-oberhelman-manufacturings-mouthpiece#p4.
[48] Lydia Depillis, “Britain’s Chamber of Commerce Says Corporations Should Share Their New Prosperity with Line Workers. Wait, What?”Washington Post , Dec. 30,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12/30/britains-chamber-of-comme rce-says-corporations-should-share-their-new-prosperity-with-line-workers-wait-what/.
[49] Eliezer Yudkowsky, “The Robots, AI, Unemployment Anti-FAQ,”LessWrong (blog),July 25, 2013, http://lesswrong.com/lw/hh4/the_robots_ai_and_unem ployment_antifaq/.
[50] King, Ian and Beth Jinks, “Icahn seeks $150 million Apple stock buyback,”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October 1, 2013. http://www.sfgate.com/business/article/Icahn seeks-150-million-Apple-stock-buyback-4860812.php.
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能产生多大的威力,安东尼·杰特曼医生每周至少有一次切身的体会。杰特曼医生就职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总医院,是一名放射肿瘤医生。杰特曼医生经常需要与前列腺癌患者见面,讨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过去的患者只会顺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取医生的治疗建议。而杰特曼医生说,如今“经常会有患者来到医生的办公室,打开一大堆网页,并且说‘我知道有这么一种疗法’”。在很多情况下,“这么一种疗法”指的是质子疗法。这种尖端的疗法通过发射一束极窄的粒子流,杀死其他疗法难以触及的部位的肿瘤,并能避免伤害肿瘤周围的健康组织。患者之所以青睐更为精确的质子疗法,是因为一些传统的治疗前列腺癌的方法有可能产生阳痿、尿失禁等副作用。然而,杰特曼医生会耐心地向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在前列腺癌的治疗方面,质子疗法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优势。事实上,质子疗法精确度高的优势只有在治疗一些高风险肿瘤(比如眼部肿瘤和脊柱肿瘤,因为在这些部位即使出现很小的误差,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时才能发挥出来。然而针对前列腺癌,质子疗法并不能提高治疗的有效性,也不会降低严重副作用发生的概率,因此与传统疗法相比,质子疗法在治疗前列腺癌方面没有优势。而该疗法的劣势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疗法的成本明显高于传统疗法,治疗费用可以达到其他疗法的2~5倍。因为用于治疗的质子束由粒子加速器产生,而这种体育馆大小的机器成本高达1.5万亿美元。 [1] 杰特曼医生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这些并无必要的治疗上,不如把钱花在更有实际意义的地方,比如对主要医疗项目的投资,或者建立新的门诊中心和手术中心。
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市场应该能自动减少甚至消除针对前列腺癌的质子疗法。然而,因为仪器制造商和医院花重金进行大量宣传,而扭曲的医疗保险系统又对疗法的成本很不敏感,近年来这种没有必要的昂贵疗法反而变得十分流行。根据预测,到21世纪20年代,美国将拥有31所质子治疗中心——这个数量达到了实际需求的三倍,于是美国的医疗系统距离全面崩溃又近了数十亿美元。杰特曼医生说:“我们根本无力负担这样的疗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每个患者都想接受质子治疗,而且不是因为这种疗法对他们更好,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疗法,他们想要享受最新、最先进、最尖端的疗法,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被这种情况搞破产。”看来,医药领域已经成了市场和自我互相融合的最新战场,商家利用我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来获得短期利益。
事实上,美国的整个医疗系统早已成了冲动的社会的加速器。医疗系统是整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如何以自己创造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为引擎,人们不断地追求各种短期、狭隘的个人利益。整个美国被一种奇怪的“健康”文化所主导。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各种不必要的疗法上毫不心疼地花费数亿美元;另一方面,至少有5 000万美国人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也买不起。这种文化鼓励人们毫无节制地追求即时的满足,据估计,如果现在的情况持续下去,我们的孙辈可能需要缴纳3倍于现在的税收,才能偿还我们这一代人积累下来的医疗债务。这种健康文化鼓励人们对医学治疗抱有一种严重夸大,甚至极端自恋的预期(至少对能够买得起医疗保险的人来说是这样的),现在的人们似乎认为任何形式的疾病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甚至鼓励人们拒绝承认自我的局限性和短暂性。我们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去抗拒一些不可抗拒的事情(美国人每年在整形美容手术上的花费是110亿美元,在睾酮凝胶上的花费是20亿美元),人们似乎相信这些尝试能够帮助他们完全逃离衰老和死亡。2013年年末,谷歌公司成立了一家新的机构——加州生命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研发新的医疗措施,将人类的寿命延长20~100年。 [2]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现在每10个美国人中有4个接受这样的医疗措施。
换句话说,美国的医疗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详尽而令人痛苦的案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后物质主义理想制度化会带来怎样的风险。从理论上说,医疗系统应该是一种保护公民不受实际风险伤害的社会系统,所谓实际风险是指患病的风险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压力。在这样的传统定义下,医疗系统帮助每个公民更好地实现个人的潜能,从而促成一种更文明、社会参与度更高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制度化的过程出了问题——美国的医疗系统显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如今美国公民只关注狭隘的个人利益,这已从整体上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发展。换句话说,在我们即将崩溃的医疗系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物质主义理想与自我和市场的冲动之间的内在张力,目前这种张力正把整个冲动的社会推向同样不利的方向。但是,当我们试图对功能失调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时,我们第一次做出了面对这种张力的尝试——我们试图冲破各种经济、政治以及心理上的壁垒,正是这些壁垒让冲动的社会看起来如此强大、如此坚不可摧。
因此,奥巴马医疗改革被视作美国这个时代最核心的英雄传奇。 [3] 虽然奥巴马推出的平价医疗法案在设计和实施方面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然而这却是美国对疯狂蔓延的后物质主义进行再平衡的首次全面尝试。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关于我们能否把冲动的社会转变为某种更人性化、更可持续的社会的争论。美国在医疗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得以瞥见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更大困难。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支持社会以某种更广泛、更长远的价值作为前进的方向,那么美国医疗文化的问题及潜力也许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哈佛大学毕业的约翰·诺尔斯医生也曾面临过同样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为阻止过度医疗进一步伤害美国的医药产业,诺尔斯医生发起了一场抵制过度医疗的公众运动。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诺尔斯医生的语调不像一名医生,而更像一位推崇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诺尔斯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很多医生对患者采取大量无必要的医疗措施并收取高昂费用的行为。诺尔斯医生说,这些医生这么做不是出于医学上的需要,而是“挖国家的钱来中饱私囊,他们这么做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想买辆新车”。 [4] 除了批评自己的同行外,诺尔斯医生也对美国医疗产业的消费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消费者的个人习惯——“暴食、酗酒、滥用药物、熬夜晚睡、滥交、超速驾驶、吸烟”也是导致美国医疗开支剧增的重要原因。 [5]
诺尔斯医生认为,美国公众的这些坏习惯部分应该归罪于我们一味放任的“信用卡文化,人们总是贪图眼前的享乐,而把成本推迟到未来。这种文化影响了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从饮酒、进食到买车、买房”。然而,诺尔斯医生认为,造成这些恶习的更大原因是一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力量,它使美国公众丧失了对自身健康负责的个人责任感。诺尔斯医生指出,一方面,美国公众要求在个人健康选择方面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 [6]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医疗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慷慨的医疗系统,公众逐渐对这样的医疗系统产生了不现实的预期,他们希望在健康方面享有无限的选择自由之后,能够依靠医疗系统解决放纵带来的所有不良后果。诺尔斯医生曾这样写道:“个人权利全面淹没了个人责任。人们希望政府可以对他们的个人权利进行担保,希望各种公共和私有的制度能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 [7] 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缺陷会鼓励人们采取不良的个体行为——这样的规律早已存在,也绝不仅限于医疗领域。事实上,这样的规律正是长期存在的关于国家和公民最佳关系模式之争的核心议题。然而,通过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极为困难。即使我们已经明确知道目前两者之间出现了失衡,要修正这种失衡仍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我们建设美国的医疗制度时,并没有将取得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完美平衡作为目标。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十分具体和现实的。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将提供全民医保作为重要政治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设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目标。美国政府于1965年推出了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两项措施,其目的是弥补美国以私有医疗保险为主的保险体系的不足。支持全民医保的人认为,这种公私结合的体系为国民提供的医疗保障严重不足。然而支持这一体系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设计能让美国人民同时享受到公共保障和私营效率的双重好处——私营市场可以提供创新的动力和市场化的规范作用,同时政府又建立了一个公共的社会安全网作为对私营市场的补充。上述两派的观点都说对了一半。在新的联邦保险计划推出之后,美国的私营医疗市场确实掀起了技术创新的高潮。由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都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支付医院和医生的费用(很快,大部分州政府也要求私营保险公司采取同样的做法),国会不仅创造了大量对医疗的新需求,还消除了医疗供应市场上存在的许多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的医疗创新迅速出现。由于医疗保险可以帮助患者支付更多的费用,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从而刺激了各种新疗法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治疗的效果大大提高。20世纪60年代,每5位心脏病发作的患者中会有3位不治身亡。然而到了2000年,由于有了β受体阻滞剂、心脏监护病房、血液稀释剂、血管形成术、血管支架等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手段,每4位心脏病发作患者中只有1位会不治身亡。 [8] 在医疗系统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巨大进步。到2000年,医疗系统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又延长了4年。 [9] 然而,新的医疗系统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后果。医保的慷慨弱化了患者维护自身健康的动力,同时也弱化了医疗服务提供者节约各种医疗资源的动力。我们使用的医疗服务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同时我们使用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下降了。在对疾病的主动预防和事先筛检方面,我们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很多疾病直到晚期才被发现。此时不仅患者的健康已经严重受损,可行的医疗方案也已经非常有限且昂贵,这就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医疗开支。此外,由于患者不必为医疗费用发愁,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总是不断要求享受更先进的医疗手段,医疗创新市场也因此出现了更严重的扭曲:我们进一步忽略了对疾病的预防,而着重研发各种更复杂的、更有利可图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也由于许多简单的治疗措施已经被研发使用了,产品研发的成本不断上升,每一代新的医疗创新成果都变得比上一代更加昂贵。
医疗创新成本的急剧上升进而导致了一种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化趋势,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详细解释过这种金融化趋势的害处。由于医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医生和医院一旦购入新的医疗设备,就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收回成本,他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些医疗设备来获取利润。在这里,我们可以以两项最常见的医学成像技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I(核磁共振)——为例。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两项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癌症和其他各种疾病,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然而,这两项技术的金融特点——高昂的前期投资(50万~300万美元)和相对低廉的运行费用——导致医生和投资者都会尽可能频繁地使用这些机器。研究医保政策与个人决策关系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米塔布·钱德拉说:“只要你花费了安装这台机器的固定成本,你就有充分的动机让每一位患者都接受这项检查。”作为两种通用的诊断工具,CT和MRI从理论上说适用于任何一种医疗情况,因此过度检查的倾向自然很难避免。钱德拉说:“问题的关键就是,医生可以让全美人民都接受CT或者MRI检查。” [10]
医疗技术行业的经济规律与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来越相似,因此医疗技术的研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模式也越来越类似于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从业人员。钱德拉说:“医疗产业的情况与航空公司的情况十分类似。如果你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当你买入一架新的波音777飞机,你当然不希望这架新飞机在停机坪上白白浪费时间。你希望这架飞机每时每刻都在飞行。”此外,由于医院和医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些成本高昂的技术,越来越多的患者也慢慢熟悉和习惯了这些医疗技术,并把它们当作常规医疗服务的核心元素。
这一切又一次导致了冲动的社会的经典矛盾:一波又一波医疗创新带来了更多的疗法和更高的期望,而更高的期望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创新。随着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人们期望着一个又一个医疗奇迹的出现。同时,这也导致了医疗开支的飞速增长。目前,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左右。支出和预算的不匹配导致医疗赤字不断上升,在美国的总体经济产出中,医疗赤字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1960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5%,而现在,虽然美国经济已经远远大于1960年的规模,医疗开支却占到了GDP的17%左右(如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公共健康上的支出超过该国GDP的12%)。 [11] 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专家预测到2020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将占到GDP的20%。目前美国医疗系统的情况像极了苹果和通用汽车的经营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永不停歇地更新换代,而区别是美国医疗系统的规模远大于任何公司。医疗伦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丹尼尔·卡拉汉就职于专门研究医疗成本的海斯廷斯研究中心,卡拉汉曾说:“美国医疗系统的情况就像太空探索一样。不管你已经到了多远的地方,永远有更遥远的太空等你去探索。美国的医疗系统仿佛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黑洞。” [12]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医疗模式以保险、创新、消费者期望为核心驱动因素。在这样的医疗模式之下,我们的医疗文化渐渐走上了一条歧途,很多极为荒唐的事情现在却成了常态。纽约市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是世界最顶尖的癌症治疗机构之一。2012年,该研究所由于拒绝引进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新药——阿柏西普而登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该研究所的这一决策如何赞美都不够:用阿柏西普治疗癌症的开支是每月11 000美元,比目前广泛使用的抗癌药物艾维坦贵不止1倍。然而在疗效方面,阿柏西普和艾维坦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事实上,艾维坦也并不是一种便宜的药品:对一位典型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一个疗程的艾维坦价格大约在8万美元。艾维坦有时会导致内出血等副作用,并且数据显示,艾维坦只能将患者的生命平均延长6周多。此外,还有另外一种针对前列腺癌的抗癌药——普罗文奇。普罗文奇每个疗程的价格大约是9.3万美元(因为制药商需要收回11亿美元的研发成本),然而这种昂贵的药品只能将患者的生命平均延长4个月。 [13]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正是这些科技进步的成果让今天的患者能够拥有更多的治疗选择。然而,我们有时也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由于失衡的医疗部门具有强烈的金融动机,每一位处在生死边缘的患者都必须面临这种可怕的两难困境。卡拉汉说:“制药公司非常清楚,不管药品的价格多么惊人,总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购买这些药品。保险公司可能愿意支付这些昂贵药物的部分开支,但很少会全额赔付。为了获得这些药品,有些患者选择卖掉自己的房子,或者这些患者的子女会卖掉自己的房子,他们为了这些药品宁愿破产。”然而在很多其他国家,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医疗保险系统是由政府运营的,公共医疗系统通常会拒绝为这种高成本、低价值的药品埋单。因此在那些国家,患者在这方面的期望值就会低很多。在英国,如果患者被诊断患有某些晚期癌症,医院会主动建议他们采取保守疗法,或者干脆建议他们搬去临终关怀机构。杰特曼医生就来自英国,据他说:“也许你会说:‘这样做岂不是太残忍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残忍,而是接受现实。在美国,我们假装可以用一些昂贵的药物来治好你的疾病,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欺骗。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来争取微不足道的时间其实是很不理智的。”
然而在美国,甚至连晚期癌症都被当作一种商业机会,患者家属通常只有在患者去世以后才会追悔莫及地想起还存在保守疗法这种选择。美国患者进入临终关怀机构的治疗时间中位数不足3周;在住进临终关怀机构的患者中,有1/3的人入院不足7天就去世了。在美国,面对晚期癌症的流行做法是进行英雄式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这通常意味着采取一些极为昂贵的治疗手段。这种文化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当政府和某些保险公司试图说服患者放弃昂贵的低效率治疗时,居然受到了严重的抗议,甚至面临法律诉讼。卡拉汉说:“在美国,这方面最保守的意见是,选择是否继续治疗的决策永远应该由患者本人做出。然而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严重患病的人常常缺乏理性选择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常常不是最好的。在我看来,一个好的系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们免受错误选择的伤害,尤其是那些事关金钱的选择,更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然而,目前的医疗系统不仅越来越无法避免患者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人们做出非理性选择。因为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这些非理性的错误选择恰恰是商家利润的来源。
显然,医疗系统能有效提供的东西与消费者的真正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差异再次表现出冲动的社会的典型弊病,要不是这种差异带来了如此令人悲痛的结果,我甚至会觉得这带有一种讽刺性的喜剧效果。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巨额投入却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健康方面的合理回报。衡量一个国家医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患者满意度等,然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美国医疗系统的表现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14]
美国医疗系统弊病的另一个主要的症状是,目前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基本的健康保险。这项统计数据在各种场合被不断提及,因此我们可能已经麻木了。然而,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多么令人震惊: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却有1/7的人口无法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现象存在。我想,美国之所以陷于这样一种可耻的境地,是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都不像美国这样完全屈服于短视和狭隘的个人利益。这种短视和对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冲动的社会的最核心特征,正是面对这些人性弱点时的妥协态度造成了如今美国基础医疗保险覆盖率严重不足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覆盖率的下降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的公司成本控制风潮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为了控制成本,很多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起不再向工资较低的员工提供医疗保险。这一举动导致了极为迅速和剧烈的社会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虽然美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但在工资较低的员工中,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数比例却比20世纪80年代时还要高。乔治城大学一位卫生保健专家朱迪思·费德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化带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教训是:不仅低迷的经济表现会降低全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繁荣的经济周期也未必会促进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回升。”
确实,如果经济的繁荣意味着医疗创新的跑步机永不停息地高速转动,这反而会导致穷人更难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险。第一,由于我们过度依赖昂贵的新技术,医疗成本必然会快速上升,这就导致穷人更加无力负担基础医疗的开支。第二,由于医疗系统的商业模式是以追求资本回报为首要目标的,这必然导致整个医疗系统倾向于那些耗费巨额资本、社会价值并不高的医疗技术。哈佛大学的钱德拉指出,目前一位患者接受一次质子疗法所产生的费用足够为三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购买医疗保险。钱德拉告诉我说:“从事实来看,这就是我们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目前选择的分配情况。我们宁愿为某些人提供昂贵的质子治疗,也不愿向另一些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制度经过审慎的权衡后做出的选择,然而我个人却很难相信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任何人愿意花两分钟以上的时间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他一定会说:‘不,这是一个疯狂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医疗选择对冲动的社会而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在冲动的社会中,医疗的目标不是公众的健康,而是医疗本身(即对疾病的治疗)。在一种理性的医疗模式下,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尽一切努力(从饮食到运动,再到预防性医药措施)保持人们的健康水平,应该是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控制,而不是等疾病严重的时候再进行大量昂贵的治疗。然而在现有的消费者环境中,这个系统的最高追求却是快速的资本回报,任何支出都被视作一种正面的经济行为而得到鼓励和表扬。在这样的评判体系中,昂贵的医疗干预确实比预防性医疗活动更有价值。我们的医疗系统已经陷入了一种十分荒谬的境地:医疗本身已变得和健康一样重要,因为医疗本身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几年前,记者兼公共政策分析师乔纳森·罗曾这样说道:“医疗系统的目标应该是更健康的民众,而不是售出更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然而,现在我们却以医疗行为而非医疗结果为标准来评判医疗系统对经济的贡献。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不久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导致疾病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新闻。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必须鼓励民众多生病,因为经济的健康迫切需要民众生病。” [15]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行医疗改革如此困难。首先,我们必须重建一系列的制度和常识,因为这影响着我们管理自身健康的态度,而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诚然,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并不缺乏先进医疗系统的范例,从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实行的由政府运营的单一付款人医疗制度,到瑞士和新加坡采用的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医疗模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系统都比美国的医疗系统要理性得多。但出于各种原因,究竟什么样的医疗模式最适合美国成了一个我们始终无法达成明确共识的难题。分歧之一是,在管理医疗这一极为重要的事项时,究竟是政府的效率更高,还是市场的效率更高(或者说危害更低)。
对支持单一付款人模式的人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很明显的:政府才是医疗服务最理性的提供者,因为政府可以利用其巨大的规模优势以最低的价格买入医疗服务,并可以利用其监管方面的权威来管理(更粗暴地说是“配给”)个人使用医疗服务的数量和程度。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应该能同时限制市场和个人消费者两方面的过度医疗倾向,医疗可以不再是一种昂贵而极易波动的消费者商品,而变成一种基本的社会服务。与此同时,这些效率方面的提高必然会帮我们省下一些资金,这些资金正好可以用来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购买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而市场模式的支持者则认为,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资金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最低标准的医疗保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虽然只拥有有限的资源,却能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这些资源,因此消费者在决定使用多少医疗服务、如何使用医疗服务时,会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这意味着更强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会迫使医院、医生以及医疗技术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一样更加重视对成本的控制。
但是,关于医疗系统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哪种系统效率更高的问题。虽然关于医疗的争论常常以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作为议题的核心,但其实这方面一直存在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仅涉及消费者与市场的关系,而且涉及公民与社会的关系(注意公民和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随着关于医疗系统最佳形式的争论的展开,我们尤其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究竟对其公民负有怎样的义务?而公民又对社会负有怎样的义务?关于这一点,就职于哈佛大学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的医疗伦理学家丹尼尔·维克勒说:“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很多其他国家已经接受的前提,即国民的健康是国家必须担负的一种责任。国家是否有义务保证国民的健康?尤其是,是否有义务保证所有需要就医的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 [16] 维克勒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是否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并找到足够的资源及合理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导致健康恶化的唯一原因是你无法负担的医疗费用,那么在你生病的时候,你的邻居是否有义务向你提供帮助)。
显然,我们还远远没有找到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在奥巴马医疗改革启动之前,虽然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支持者的比例是56% ,而反对者的比例是33%),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医疗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降低成本,而不是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 [17] 这样的民意至少部分反映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显然公众对一系列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安全网络是否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然而,乔治城大学的费德指出,这样的民意同时也显示出医疗行业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人们保持现状的愿望。目前的事实显示,虽然美国的医疗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对他们目前的医疗状况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大部分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获得需要的医疗服务。对美国大多数民众而言,有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事实让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也并不反对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医疗状况。费德说:“推行全民医保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医疗保险,而我们不希望自己目前享受的医疗保险受到影响,毕竟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只是少数。”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美国政府也曾试图推行医疗系统的改革,然而那次改革的动议却以失败告终。费德曾经亲身参与克林顿政府的这项工作。他告诉我,正是因为公众极不希望自己目前所享受的医疗保障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曾经积极鼓吹单一付款人模式的民主党议员现在已经很少再提起这一医疗模式了。费德告诉我说:“消费者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维持现状。”正因如此,在奥巴马医疗改革出台之前,大部分医疗改进措施的核心不是任何形式的变革,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福利:比如,2003年曾通过一项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法案,这项福利在民众中很受欢迎,却也导致了高昂的政府开支。
正因为公众这种集体性自我保护意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大规模的负面情绪早已超出了对拙劣部署的反感所能解释的程度。奥巴马的平价医疗虽然保留了美国医疗系统公私结合的基本结构,但仍从很多方面对一些关键制度导致的不良医疗行为进行了限制和惩罚。比如,联邦医疗保险的支付结构发生了改变,医疗服务提供商能收到的款项不再取决于它们提供了多少医疗服务,而是取决于其治疗效果。这一变化目前已经成功降低了联邦医疗保险项目的开支,几十年来,美国医疗成本的上涨速度首次出现了减缓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很可能是得益于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还包括一项名为“比较效率审核”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保险公司有权拒绝那些性价比过低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程序(在英国等国家的单一付款人医疗系统中,这是一项标准化的重要特征)。 [18] 更富争议的是,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提高了个人和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的价格,使得消费者和雇主必须承受更多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消费者和雇主因此必须接受更多市场约束。此外,平价医疗法案还包括一项个人强制保险规定,根据这项规定,所有目前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的人(这些人通常是健康状况较好的年轻人),都必须强制购买医疗保险,他们所付的保险费将被存入整个医疗系统的“风险池”,为他们日后需要医疗保障时做准备。从理论上来说,个人强制保险规定能够修正个人自然的短视特点,不致为社会带来高昂的成本。
尽管如此,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做出的这些改变可能还称不上真正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并未触及美国医疗系统的核心问题:不合理的公私结合模式。尽管如此,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仍然对美国医疗系统的现状起到了显著的修正作用,也清晰地回应了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争论,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见到效果。随着支付政策的改变,随着医生和医院改变对各种治疗手段的态度,未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联邦医疗开支的人均成本显著下降。同时,过度追求医疗技术更新的“强迫症”很可能也会有所缓解,美国将不再是一个质子疗法的国度。
然而,关于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效果,也存在一些不那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分歧。比如,对那些由联邦医疗保险全额赔付的医疗技术,法案设置了赔付上限,此举是否会导致减缓医疗创新速度的不良后果呢?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医疗制度都能在某些情况下禁止本国医生使用过于昂贵的治疗手段,但这两个国家的患者仍然能享受到很多最前沿的医疗技术,而这些医疗技术的创新成果恰恰是由美国公私结合的创新体制产生的。这方面的担忧已经超出了医疗领域的范畴。更根本性的是,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措施最终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后坐力?当美国国会于1965年推出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两项措施时,保守派曾对这两项福利措施进行过强烈的反对和阻挠。然而,这些反对和阻挠并未阻止这两项福利措施的推行,这部分是因为当时强有力的民主党占多数,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当时快速老龄化的美国社会发自内心地欢迎这些福利的出台,而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具备足够的财力对老年人进行上述补助。然而在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推出的今天,美国社会已不复当年的富裕与繁荣。因此,国家无力承担医疗改革的全部成本,法案的推出意味着很多群体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或者享受更少的福利。虽然在法案实施的过程中,前期部署方面的缺陷以及保险取消问题已经激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负面反应,然而随着这一法案改变美国医疗现状的长期效应逐步显现,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选民爆发出更强烈的愤怒与反对。
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为目前没有医疗保障的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开支很大一部分来自联邦医保支出的削减。长期研究政府政策的专家托马斯·埃兹尔认为,扩大保险覆盖率的受益人群主要是穷人和少数族群,而联邦医疗保险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中产阶级和白人。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公共资金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群体的获利意味着其他群体的损失。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再分配选择。埃兹尔警告我们,这一过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很可能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和选举方面的影响。2013年11月,埃兹尔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相关文章,文章指出:“由于对纳税人的税金和其他公共资源进行了再分配,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而穷人和少数族群则获得了实惠,大部分白人选民势必表示反对。很多人认为,白人选民的反对和阻力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只要回头看看2010年的选举情况,就会发现白人选民的不满情绪会导致重要的政治后果。在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当年,这种反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共和党人迅速占据了美国众议院以及各州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目前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遇到的种种困难都明确告诉我们,2010年的情况很可能会在2014年甚至2016年(大选年)重演。” [19]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靠政府的强制权力来限制驱动冲动的社会的各种不良反应(包括医疗、金融以及个人行为方面的不良反应),我们就应该预测到政府强权的使用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坐力,因为冲动的社会一定会拼死捍卫自身的利益。
奥巴马医疗法案试图极大地改变美国社会的现状,从某些角度看,与这一改革的雄心相比,改革受到的反对可算是相当轻微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奥巴马医疗法案距离他们梦想已久的欧洲单一付款人模式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很多保守主义者则担心,奥巴马医疗法案是几十年来将美国社会推回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经济管理模式的首次努力,而这种经济管理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该被斩草除根了。更根本的是,奥巴马医疗改革所遭遇的阻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条我们历来珍视的信念:美国人愿意为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而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十年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升温以及高度响应型消费者经济的洗礼,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对个人牺牲的抗拒已经成了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大阻力之一。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自私的行为却是一种习得行为。毫无疑问,过去几代美国人比现在的美国人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然而不幸的是,正像冲动的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的医疗文化不断滚动着创新与期望的正反馈雪球,这种反馈机制事实上培养了人们不懂感恩的自私品行,让人们把一切权力和福利都视作理所应得的东西。于是,当保险公司拒绝为昂贵的实验性疗法埋单时,有些患者愤怒地采取了诉讼的手段。甚至有些患者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提高自己在器官移植分配系统中的优先级。这种行为的实质是,人们希望绕过制度和规范的限制,为自己争取稀缺的医疗资源,而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希望这些稀缺的医疗资源能够被平等地分配。在美国,这类挑战制度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在英国等其他国家,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在英国等其他国家,政府的医疗政策比美国更严格,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制度和规范的接受和遵守程度也比美国人高得多。乔治城大学医疗中心的一位医生兼生命伦理学专家凯文·多诺万告诉我:“英国人比我们更懂得排队——他们能更好地接受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并且能在队列中安静地等待。而美国人在排队问题上的态度则是:‘任何限制一定有合理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遵守这些限制——除非我自己受到限制。’” [20]
事实上,在美国的医疗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固有偏差,而仅仅依靠政府的改革是很难完全消除这种偏差的。我们对医疗技术的狂热追求人为地催生了这种偏差,而这种偏差显示了广义的冲动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主要挑战。大部分疗效神奇的医疗创新成果都非常昂贵。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呼之欲出的基因靶向治疗,这种治疗意味着生物技术公司可以针对某种特定的疾病为患者量身定做极有针对性的药物,而这种先进的治疗手段通常只针对总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哈佛大学的钱德拉指出,因为基因靶向治疗技术的研发非常高昂,投资者为了快速收回成本,必须迫使生物技术公司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困扰富裕人群的疾病上。这就意味着这些先进技术的目标受众不仅是富裕国家,而且是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精英阶层。钱德拉告诉我:“研发这种药物的公司更可能以美国市场为目标,而不会以阿富汗和斯里兰卡之类的国家为目标。而在美国国内,这些技术的目标受众更可能是波士顿和曼哈顿的富裕人群,而不是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的穷人或患者。”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也许我们很快就能识别各种影响人们智力、野心及其他决定人们富裕程度的基因片段。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基因档案进行扫描,筛查出每个人易患的疾病,并及早进行预防和干预。这种分拣技术将在分子水平上继续发展。
然而,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意味着巨大的研发成本,同时我们的医疗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狂热地追求快速的资本回报。不难想象,医疗系统的未来会与现在的情况高度相似——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医疗创新成果将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负担这些技术的富裕人群市场。即便我们能够将美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为单一付款人模式,我们的医疗文化仍然会像泰勒·考恩在《再见,平庸时代》中所描述的那样,呈现高度两极分化的特点。富裕人群不仅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可以率先享受那些能显著延长人类寿命的创新成果带来的好处。30年后,如果考恩所描述的“超级劳动者”不仅比其他人更富裕,而且比其他人活得更久,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的医疗文化一再强调并加速着冲动的社会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均衡现象,也不断塑造着各种影响我们决策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否带领我们抵达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这些技术创新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取舍?——我们很少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高速前进,如何获得即时回报与满足。医药科学的进步帮助我们消除了很多影响人类寿命的疾病,这当然是一件令大多数人感到欣喜的事情。然而,随着我们的生命变得更长,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长寿会为我们增添很多不可忽视的成本——而我们在构想医疗体系时,却未能理性地将这些成本列入考量的范围。平均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患上各种导致我们无法自理的慢性疾病,比如癌症、中风、阿尔茨海默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和护理都是非常昂贵的。即便是无病无灾的长寿者(他们无病的晚年可能是得益于非常好的运气,也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某种神奇的“超级治疗”)也无法逃脱高龄的必然结局——虚弱和衰退。这种不可避免的虚弱和衰退常常把长寿者最后的年月变成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漫长折磨。华盛顿的一位老年病专家乔安娜·林恩是医疗改革的直接执行者,她将这种长寿者的状态形容为“像被凌迟处死,因为对这些长寿者来说,仅仅维持每日的基本生活便必须克服各种越来越痛苦的困难”。 [21]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衰老所引起的虚弱以及各种使人丧失自理能力的慢性疾病将成为各大后工业化、后物质主义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显然,这并不是我们规划中的医疗未来。如果我们能够预见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更早开始对各种医疗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我们会更努力地帮助老年人与虚弱和衰退做斗争——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意味着我们的着眼点不是临终治疗方案,而是各种看起来更加微不足道的日常关怀,比如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所需的交通工具、合理的营养,或者护士的上门看护。然而事实上,我们目前的医疗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忽视了老年人的这些基本需求,却把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放在研究能延长生命的医疗创新方面。不可否认,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受金钱利益的驱动,因为这些试图延长生命的创新远比上述日常关怀更能为医疗系统提供丰厚的利润。
与此同时,这种扭曲的文化已经开始惩罚我们——我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身的局限,越来越无法接受自我的短暂性,我们甚至会极力回避这一点。虽然各种医疗创新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但当一切神奇的续命疗法用尽时,每个人最终还是必须面对走向死亡的时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医疗创新的巨大成功导致个体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样的时刻。在永不停歇的医疗跑步机的驱动下,我们处理衰老与死亡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公开、越来越欠考虑。我们越来越难以靠个人信念和文化传统的引导渡过死亡的难关,甚至越来越拒绝承认和接受死亡的宿命。当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我们越来越在执念的驱使下无谓地拖延时间,而培植这种执念的正是医疗市场的结构性“本能”,是各种各样的资本循环和靠临终治疗牟利的商业跑步机。衰老和死亡本应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本应是展现优雅、人性和勇气的伟大时刻,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衰老和死亡却成了另一种未被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成了另一种未被实现的消费者欲望,成了市场试图确认自我的伟大和永恒的又一次失败尝试。
显然,这又是冲动的社会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自恋型人格的人尤其难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因为这类人的自我是如此膨胀,仅仅是想到他们的自我将不复存在,就足以使他们陷入极度恐惧之中。因此自恋型人格的人会用尽一切方法否认和避免死亡的来临。作为冲动的社会的一员,自恋是我们的集体性格,因此我们对死亡怀着同样非理性的恐惧和抗拒。随着延长生命技术的每一点进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变得更深刻、更令我们动弹不得。
因此,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实际上为冲动的社会提供了最清晰的预后分析。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面对各方面的危机:医疗问题、金融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崩坏的问题。然而,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危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是在冲动的社会中,我们面对和处理这些危机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丧失。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由于我们早已习惯了高度个人化的经济模式,我们既不愿意延迟满足,也完全拒绝任何可能让我们脱离舒适区的事物。然而,更严重的是,曾经帮助我们克服和限制这些个人缺点的公共制度(主要是我们的媒体和政治体系)也已经因为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腐蚀而变得极度脆弱,从而丧失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1] “Benef its, Cost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of Proton Therapy,”Asco Daily News ,June 1, 2013, http://am.asco.org/benef its-cost-and-policy-considerations-proton-therapy.
[2] Dani Fankhauser, “Google Wants You to Live 170 Years,” Oct. 24, 2013, Mashable.com, http://mashable.com/2013/10/24/google-calico/; and Harry McCracken and Lev Grossman, “Google vs. Death,”Time , Sept. 30, 2013,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printout/0,8816,2152422,00.html.
[3] Amy Goldstein and Juliet Eilperin, “Healthcare.gov: How Political Fear Was Pitted against Technical Needs,”Washington Post , Nov. 3,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politics/challenges-have-dogged-obamas-health-plan-since-2010/2013/11/02/453fba 42-426b-11e3-a624-41d661b0bb78_print.html.
[4] Lee Wohlfert, “Dr. John Knowles Diagnoses U.S. Medicine,”People , May 6, 1974,http://www.people.com/people/archive/article/0,,20064026,00.html.
[5] John Knowl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Daedalus 106, No. 1, The MIT Press (Winter 1977): p. 59.
[6] Ibid., p. 75.
[7] Ibid., p. 59.
[8] David Brown, “A Case of Getting What You Pay For: With Heart Attack Treatments,as Quality Rises, So Does Cost,”The Washington Post , July 2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7/25/AR2009072502381_pf.html.
[9] David M. Cutler and Mark McClellan, “I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cine Worth It?”Health Affairs 2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11–29.
[10] Interview with author.
[11] Fareed Zakaria, “Health Insurance Is for Everyone,”Fareed Zakaria (blog),March 19, 2012, http://fareedzakaria.com/2012/03/19/health-insurance-is-for-everyone/.
[12] Interview with author.
[13] Courtney Hutchison, “Provenge Cancer Vaccine: Can You Put a Price on Delaying Death?” ABCNews, July 29, 2010, http://abcnews.go.com/Health /Prostate Cancer News/provenge-cancer-vaccine-months-life-worth-100k/story?id=11269159.
[14] Zakaria, “Health Insurance Is for Everyone.”
[15] Jonathan Rowe, “Our Phony Economy,”Harper’s , June 2008, http://harpers.org/print/?pid=85583.
[16] Interview with author.
[17] Jeffrey M. Jones, “Majority in U.S. Favors Healthcare Reform This Year,” Gallup,July 14, 2009, http://www.gallup.com/poll/121664/majority-favors-healthcare-reform this-year.aspx.
[18] Benjamin Zycher, “Obamacare Inhibits Medical Technology,”Washington Times ,Jan. 9, 2012,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jan/9/obamacare-inhibits medical-technology/.
[19] Thomas B. Edsall, “The Obamacare Crisis,”New York Times , Nov. 1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1/20/opinion/edsall-the-obamacare-crisis.html?pagewanted=1&_r=2&smid=tw-share&&pagewanted=all.
[20] Interview with author.
[21] Interview with author..
2009年1月20日晚,奥巴马在美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完成了就职宣誓。然而,在总统就职仪式结束仅仅几个小时后,十几名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就在华盛顿的一家名为“核心会议室”的餐馆里举行了一次紧急的战略会议。 [1] 这次紧急会议包括一顿3小时的晚餐和很多瓶葡萄酒,与会人士包括共和党的很多重要人物:众议员埃里克·坎托、保罗·瑞恩,参议员吉姆·德敏特、琼·凯尔,以及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这些共和党要员在这次会议上剖析了本次选举中共和党遭遇巨大失利的原因,并且制订了对民主党进行反击的计划,一位与会者事后将这项反击计划称为一项“起义”计划。从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天开始,共和党人就不遗余力地使用一切手段阻挠奥巴马政府议程的实施。在之后进行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共和党人对奥巴马选择的财政部部长人选蒂莫西·盖特纳的个人财务状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在众议院中,共和党人则极力阻挠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 [2] 与此同时,共和党还大量发布竞选宣传风格的广告,挖空心思地用各种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来攻击民主党的立法委员们。共和党的这场“起义”严重违反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在新总统刚刚就职时,两党应该共度一段政治上的“蜜月期”。在此期间,在大选中落败的政党至少会暂时性地配合执政党完成各项政治任务。而共和党的这种新的斗争策略被称为“核心会议室”策略,在这样的策略下,共和党拒绝对执政的民主党进行任何形式的配合。众议员凯文·麦卡锡曾这样宣称:“如果你表现得像少数派一样,那你就将永远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3] 我们将会与民主党斗争到底,我们会在每一项法案的通过以及每一项运动的进行中,尽一切可能给民主党制造挑战和麻烦。” [4]
按照这些共和党人的说法,剩下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共和党人的这种起义精神传遍了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民运动,也创造出了所谓的“茶党”组织——该组织成员的最大特点是对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行为进行积极的强烈反对。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不少起义派的候选人依靠激进派的政治活动家的运作和一些富裕的极端保守派人士的金钱资助赢得了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也获得了大量席位。从那一天开始,这些起义派人士便开始疯狂地进行各种立法运动,阻挠奥巴马政府的大部分政策(尤其是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而在这一过程中,保守派的脱口秀主持人们一直在为这场起义活动加油叫好。这场可怕的两党战争持续了4年半,对美国的各项内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和损害,并且在2013年逼迫美国政府关门了16天,使得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场两党之间的战争是美国政治体系自美国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失灵,甚至连很多美国的保守派人士都被起义派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国家利益的狭隘行为所震惊。2013年10月,共和党领导人终于否决了茶党的要求,结束了长达16天的政府停摆,这时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整个美国都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可悲的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确信,2009年的这种荒谬的两党分歧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以某些其他形式重演。导致这场严重两党分歧的所有政治因素,比如奥巴马医疗改革以及关于移民问题的改革,目前都仍然存在。支持茶党的富有的商业领袖们依然仇恨着大政府、各种政府管制规章以及针对富人的税收。此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的低迷之中。疲软的经济让有史以来最大比例的群众感觉自己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美国政府压迫和背叛了他们,对政府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导致这部分人群随时愿意以各种手段与政府对立。在这样的情绪下,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义派目前正在激烈反对或者未来即将激烈反对的很多政府动议(比如医疗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一些有望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改革措施。因此起义派的这些激进行为事实上只会进一步延长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在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恰恰是起义活动的最大燃料。换句话说,早已占据了美国现代生活其他领域的这种短视和狭隘自我利益的恶性循环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对此,我只能无奈地说,欢迎大家来到冲动的政治世界。
在这出政治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现实:长期以来,美国的保守派一直希望通过市场的约束力量重新整合美国的社会。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为了阻止这种重新整合,政府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开分歧点燃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战火。这种野蛮的斗争之火越烧越烈,漫长的两党之争意味着各个环节中的无谓拉锯,导致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然而,在党派之争的背后,是一种远非意识形态分歧能够解释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问题与冲动的社会永远不停运转的跑步机有很大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在事实上已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所控制。共和党曾被视为商业阶级的政党,而如今甚至连民主党和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也越来越把商业阶级(特别是金融板块)当作其政治机器的核心合作伙伴,因为这样的政治机器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依赖科技。在每一轮的大选周期中,美国的政治机器都在变得更加商业化。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严重依赖资本的注入(一轮总统竞选运动常常需要耗费10亿美元的巨资),因此,两党都日益成为金融市场的附庸,政治活动不仅被市场的目标和追求所控制,而且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与市场相同的周期与性质。
商业对政治的侵蚀绝不仅仅表现为职业政客所受到的腐蚀。极端主义的倾向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健康,虽然很多选民对这一点感到极度不满,然而事实上我们自身参与政治的形式也在变得日益个人化和极端化。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参与政治已经不再意味着通过努力达成妥协和共识,也不再是一种为了某种比我们的自我更加广阔的东西而投身社会的过程。对于很多人来说,对政治的参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进行个性化消费的渠道,通过消费政治党派精心制造的、分歧巨大的政治信息,参政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建立自我认知的机会。
以上现象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文化已经变得与我们的金融板块及消费者经济体一样短视。虽然我们在追求短期政治目标(比如筹集竞选资金,或者巧妙地挑选出能改变民意结果、扩大选民基础的15秒钟“言论摘要” [5] )方面正变得越来越高效,我们却逐渐丧失了利用政治过程解决某些复杂长期挑战的能力。这些变化导致我们的政治体系终日沉醉于政治本身,而已经无力解决任何其他问题。总统选举已变得像军事入侵一样复杂和激进,像IPO(首次公开募股)一样需要充沛的资金支持。牢不可破的精英阶层能够轻松地在政治活动的后台构建起隐形的精妙支持网络,让他们的短期利益得到充分的满足。美国正面临着一些复杂的、持久的问题,比如失去支撑的劳动力市场、即将破产的医疗系统、年久失修的基础建设系统,再比如注定会走向下一次崩溃的自杀式金融市场——这些问题如今已经严重威胁美国经济繁荣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的政治体系面对这些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冲动的社会的终极悲剧:唯一可以帮助我们修正短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谬误的制度,本身也已经被短期狭隘自我利益的病毒所感染,因此我们面对着毁灭性的危险却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公平地说,美国政治体系的某些失灵现象并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在20世纪的前2/3时间中,美国的政治体系取得了长期的胜利——我们鼓起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我们积极投资于国家的未来,我们成功限制了工业化经济模型的过剩倾向,并取得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政治成果——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庸的政治体系仅靠运气就可以取得的。我们英勇地挺过了大萧条和二战的困难,从这些磨难中重生的美国不仅表现出惊人的富裕和强大,还拥有着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并对极左或极右的激进主义思想抱有高度审慎的警惕态度。虽然各种严重的社会张力仍然存在,但就总体的公开政治文化而言,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相当稳健的中立主义者。美国的选民甚至常常在选举中采取“分票”手段,即将两党中的一党候选人选为总统,而让另一党控制国会。在立法过程中,两党合作现象相对现在来说可以算是非常普遍。(在1965年,虽然共和党声称民主党推行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但仍然有近半数的共和党政客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投了赞成票。 [6] )然而,这种凝聚力和两党共识的丧失却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上的党派分歧已经开始加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以及一系列的政府失灵现象和丑闻(包括越南战争、种族暴乱、失去控制的国家预算赤字以及水门事件等)打击了美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理想,也使得民众丧失了对大政府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的信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我们之前所取得的政治胜利(尤其是公民权利方面的进步)激起了保守派的反扑,进一步腐蚀了美国战后的凝聚力以及两党共识。
然而,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美国政治的党派分歧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成因是人为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选择向效率市场的意识形态靠拢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有意识地将美国社会推回向一种更古老、更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共同价值和集体主义的生存空间则因此大大减小了。政府放松了对公司的管制,于是公司可以自由地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对其他社会价值(比如员工福利以及对社区活力的贡献)的传统追求。美国公司这种新的个性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抬头,也侵蚀了美国社会中残存的战后凝聚力和共同价值。与此同时,曾经在公司与劳动者之间、市场与社区之间扮演经济裁判角色的美国政府也放弃了这种有益的身份,于是社会凝聚力的另一大主要来源也丧失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文化开始鼓励个体尽情地最大化个人的享受和自我利益。这种文化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人权力,并允许公民从社会生活中抽离,从传统价值规范(比如自我约束以及为社区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等)中抽离。我们旧式的、效率相对较低的经济体系曾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公共性的、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然而当市场赋予我们撤退的权力,我们便迅速拥抱了这项权力,转而追求一种更加个性化的生活,然而这种个性化的生活却也常常意味着更加孤立且与社会隔离。
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简要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很多美国人选择搬去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偏好完全符合的社区生活,这种行为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分类现象的加剧。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地域个性化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地图:很多曾经相对中立(即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的人数相对接近)的州和选区已经变成了深红或深蓝区域。 [7]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分类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物理世界中。随着广播谈话节目、有线电视新闻以及在线网站等各种新的媒体形式的发展,我们通过选择各种截然不同的媒体环境进一步巩固着政治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就像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分类的趋势事实上受到两种因素的共同驱动:一是我们自身的冲动的驱使,二是市场对我们的迎合——市场不断提高着满足我们上述冲动的能力和效率。就算选民不去有意追求个人化的政治环境,这些政治环境也会主动去寻求选民。以媒体为例,各种新闻渠道不遗余力地试图适应受众的偏好,这在事实上鼓励了我们这种强调差别和分歧的新型政治文化,因为这种分歧的文化更有利于商家追求利润。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众通常有着非常不同的消费模式,广告商愿意花费巨资向不同政治偏好的受众推送不同的商业广告。于是极端化的政治新闻便成了一种筛选偏好类似的受众群体的工具,这种高效率的媒体运营模式能满足商家的广告推送需求,因此具有极大的赢利潜质。靠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来区隔受众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方面的先驱——福克斯新闻频道已经筛选、培育出了大量保守派的忠实受众。根据共和党的一位媒体专家戴维·弗鲁姆的说法,福克斯新闻频道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两步策略:第一步是激起观众义愤的狂热情绪(这可以令观众继续收看该频道),第二步是制造观众对所有其他信息来源的不信任感(于是观众永远不会转向其他频道)。 [8] 如今,保守派新闻媒体仍然是这方面的高手:自由派的最主要新闻频道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观众只有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半不到; [9] 而在广播谈话节目的世界中,右派也几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10] 然而,不管从何种角度看,两极化的政治新闻都已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流,这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于那种“义愤的狂热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制造这种狂热情绪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有创意、越来越得心应手。 [11] 当然,事实上这种义愤的狂热情绪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情绪。美国的普通选民很可能并不如政客、专家以及媒体观察者所声称的那样极端。也许,媒体中的那些煽动性的修辞以及巧妙的言论摘要并不能真正反映我们大部分人对政治议题的看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宣传手法确实拥有几乎不可抗拒的极高宣传效率: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收看这样的新闻不仅更加简单轻松,而且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情感上的满足——毕竟直接拥抱简单粗暴的狂热情绪远比时刻清醒地详细分析各种政治议题要容易得多了。正像在冲动的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一样,我们最终总是会选择那条走起来最简单轻松的道路,于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换句话说,如今的政治完全变成了一种品牌。在消费者经济最初的日子里,市场营销专家就已经发现,消费者都非常喜欢强有力的“著名品牌”,否则我们在每一次购物时都必须认真分析各种厂商的宣传,再做出选择,而品牌效应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一举动所带来的焦虑感。于是在冲动的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今的政治文化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从前,保守派和自由派等字眼意味着复杂的政治概念,而如今,这些政治概念都被提炼成为一些极度简单却非常强有力的品牌。对选民而言,这些品牌的存在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和快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政治问题,而且还能让我们在道德和情绪上获得高度的确定性:我们总是坚定地相信,我方是正义的、善良的,而对方是错误的、邪恶的。对于两党的政治势力和商业化的媒体行业而言,这种品牌效应提供了一种收获选民好感的高效率途径,并且这种好感可以被很容易地转化为选票和排名。如今,市场营销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的政党运营的模式与资金充足的公共关系公司并无二致,而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都希望鼓励选民们将政治当作另一种表达自我、创造自我身份以及获得情感满足的途径。
然而,这些现象对民主制度本身而言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政治制度当成消费者经济的一个普通部分,当我们用高度商业化的方式来运营我们的政治体系,当我们把资本和感情上的效率当作政治活动的重点,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将美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变成了一场灾难。因为,公民的政治决策显然不应仅仅被当作一种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政治的决策应该是反消费主义的,也就是说在做出政治方面的决策时,我们至少应该试图超越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个人目标,应该试图抗拒非理性的“义愤的狂热情绪”,我们应该避免我们在政治上的热情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然而,由于这种令人窒息的狂热情绪恰恰是产出快速政治回报的最高效率的途径,而美国现代化的政党已经和现代化的公司一样,永远对快速的回报贪得无厌,于是狂热和极端主义变成了我们政治经济体的主要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迟或早地必然会创造出一台新型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机,这台机器的产出不是共识和进步,而是分歧和瘫痪。因此,政治市场的工业化过程必然会导致左派和右派意见分歧的加剧,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们便会觉得目前美国政界的种种乱象实在是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关于选民态度的研究显示,从1972—2008年,对于一系列核心议题,美国一位中立的共和党选民与一位中立的民主党选民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几乎扩大了一倍(意识形态差距的度量采用标准化的7分意识形态标尺)。 [12] 埃默里大学的政治科学家艾伦·阿布拉莫维茨说:“在这36年间,民主党选民从‘中立稍微偏左’移动到了‘明显偏左’,而本来已经‘明显偏右’的共和党选民则进一步向右侧移动。” [13] 简单来说,虽然共和党选民移动的幅度更大一些(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罗斯福新政经济政策现状的不满所导致的),但是两党的选民显然都比过去更加远离政治上的绝对中立态度。这种向两极移动的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两党的选民越是远离传统的中立态度,两派之间在关键问题上互相妥协的意愿就越低,而愿意妥协的政治家也就越难以获得选民的支持。
市场促成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很多层面上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纯粹的文化层面上,我们可能已经达到了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两极分化程度最高的时刻。研究美国政治地图变化现象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阿布拉莫维茨说,“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愿意与‘另一边’的人进行交流”,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之下,“人们干脆选择避免进行这样的对话,选择避免接触与他们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与立场不同的人交往会令人们不舒服,会令人们不快”。 [14]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一个十分切题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5%的美国人关心自己的子女是否会选择支持另一党派的配偶。而如今,1/3的民主党选民以及1/2的共和党选民都认为,支持不同党派的男女缔结婚姻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 [15]
美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出现了极为深刻的裂痕,人们对一些极其基本的问题(比如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以及虚假竞选广告是否道德)也已经不再能达成共识。甚至关于“是否存在一种普适的真理”这一问题也已经出现了争议。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迈克尔·林奇。林奇说:“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分歧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价值观的分歧,甚至面对事实的认知都产生了分歧。对于‘如何获得事实’,以及‘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我们和他们都无法统一。”林奇认为,当我们到达目前这种境界,民主制度本身已经受到了威胁,“因为一旦没有了对知识的共同标准,就不可能对任何事情形成共同的标准。如果两派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表,那么我们就像说着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一样。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沟通来讨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了”。
这种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式 [16] 的冲突毫不走样地投射到了美国的国家政治文化中。阿布拉莫维茨以及其他观察者都认为,这种文化已经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国会议员,这些政客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更为极端,而在立法的过程中则比我们能够回忆起的任何一代政客都更加无能。曾经,共和党中的中立派甚至比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还更加偏左,而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中立派都能够通过妥协达成两党间的合作。而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加糟糕的是,由于目前美国红色州和蓝色州的数目相当,而每一次的大选都有可能改变国会的权力平衡,于是每次的立法投票都变成了一场战略性的“赢家通吃”的机会,两党都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安抚自己在下次大选中的潜在支持者,同时也想让对手没有机会去取悦他们的选民。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参议院中,两党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冗长的辩论来阻挠对方党派法案的通过,或者抵制对方党派推举的法官候选人。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每年大约只能见到10次这样的冗长辩论。 [17] 然而到了共和党人发起“起义”的2013年,通过冗长辩论来阻挠法案的情况已经上升到了大约每年70次。阿布拉莫维茨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境地:两党几乎想用冗长的辩论来阻挠任何法案的通过,大家完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阻挠而阻挠。很多时候,两党事实上对候选人或者某项特定的政策根本不存在分歧,但他们仍然选择极力阻挠对方。这么做只是为了恐吓对手,我们的政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场游戏。”显然,这些行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日益丧失了处理真正问题的能力,甚至连推行一些非常简单的政策也很难完成,更不用提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了,比如国家债务的削减、移民问题、清洁能源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问题本是联邦政府应该重点处理的问题,而事实上美国的政治体系面对这些问题是束手无策的。
在一种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下,政治领袖应该努力而富有创造性地试图修补这样的裂痕,试图淡化选民间的分歧。即使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也至少应该试图让更多的民众回到中立的立场上,以创造出一群能够被领导的大多数。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政治领袖不仅需要对他们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行适当的妥协,而且必须启发和说服民众不能仅仅着眼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国家利益——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期间,美国的政治家们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由于消费者市场的战略腐蚀了美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多的现代政治家不仅对目前选民两极分化的局面表示非常满意,甚至还发现积极鼓励选民进一步采取极端的政见以及进一步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是一种方便而又有利可图的政治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政治竞选运动作为例子。阵营分明的“他们与我们的战斗”性质的竞选策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的政治策略家就曾使用种族作为一种微妙的手段,来刺激南方保守派人士对民主党产生敌意。然而,现在的政治竞选运动已经把这种阵营分明的宣传战略变成了一种科学的机制,这种营销手段已经取得了和消费者市场营销同样的极高效率——事实上,这些政治运动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其所雇用的专家很可能是与消费者市场营销领域完全一样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市场营销专家都开始使用消费者心理学作为争取某些特殊人口群体(比如足球母亲、福音派人士、从联邦医疗保险系统中获益的老年人)的工具,这些营销策略主要抓住那些能够激起这些特定人群热情的议题来做文章。由于政治运动的复杂性不断上升,两党都必须招募新型的专业政治人员,比如竞选咨询师。而对于竞选咨询师而言,取得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帮助雇主取得迅捷的胜利,因为没有人会愿意雇用一名看起来就会失败的咨询师。这样的情况又给我们的政治运动引入了一种新的效率元素:候选人在进行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时候,越来越愿意采取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左得多或者右得多的立场(当然,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从咨询师处获得了完全一样的建议),因为极端的政治立场是保证竞选者能快速赢得选举的最高效的武器。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党迅速发现,在宣传中使用激烈的措辞、阵营分明的宣传立场,以及推送攻击对手的负面广告是激起选民基础的热烈情绪以及获得竞选资金的最高效率的手段。政治评论家史蒂芬·珀尔斯坦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快会产生正反馈效应,从而导致更多的负面广告,以及选举日中更为复杂精妙的‘动员选票’活动 [18] 。这种能够不断自我加强的循环机制向政客们提供了很强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政客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中立立场,转而长期采取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平和中立的立场以及妥协的手段根本无法起到煽动选民基础的作用。” [19]
接下来,在21世纪初,我们迎来了大数据技术的浪潮。有了大数据技术,政党就可以针对每位个人选民的特点进行充分个性化的分化和争取工作。政治家们从大型消费者产品公司借来了这些先进的技术,手中有了这样的武器,他们不仅可以根据年龄、党派、投票历史等因素对选民进行划分和归类,甚至还可以通过更多五花八门的因素来判断选民的偏好和倾向,这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信用历史、对车辆的偏好、杂志订阅情况、电视节目收看习惯、衣着偏好、收看新闻的信息源、喜爱的啤酒品牌、枪支的拥有情况以及数百种其他各种变量。通过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进行挖掘,竞选专家们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选民对几乎所有政治议题的反应,因此他们可以设计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并通过向选民传递这些信息来试图以最高的概率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政治零售业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峰,政治市场对公民自我的入侵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2004年布什对克里的总统竞争中,布什的总策略师卡尔·罗夫就曾依靠这种精确的微观定位技术争取到了数百万2000年大选时未参与投票的社会保守人士以及福音派人士,而这群选民的支持正是布什在本次大选中获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卡尔·罗夫通过大数据技术筛选出最能引导选民支持布什的政治议题,比如同性恋婚姻和堕胎合法化问题,并据此向每位选民发送高度个性化的政治信息。 [20] 民主党则立刻意识到,2004年大选中的落败是因为它们在大数据方面未能占得先机,于是它们迅速在这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迎头赶上了共和党。到了2008年和2012年,在奥巴马总统的两次竞选活动中,他的团队都从谷歌、脸书、推特、Craigslist(一家分类广告网站)等科技公司雇用了大批数据专家。 [21] 这些专家带领的团队从所有能够想到的信息来源收集了以太字节计的海量个人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找到了每一位有可能会被说服投票给奥巴马的选民;接下来,他们继续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计算出争取这些选民的最高效途径,并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争取每一位选民。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计算和分析成为制胜的秘籍。在发送募集助选资金的电子邮件时,怎样设计标题才能起到最佳的募款效果?(专家至少测试过上千种不同标题的效果。)在给选民打电话的时候,怎样的台词最能鼓励选民去注册投票?如果脸谱网上的一位朋友邀请选民参加投票,选民接受这种邀请的概率有多大?(实验和分析的结果是,在被脸谱网上的朋友邀请后,约有1/5的受邀选民愿意去投票。 [22] )每一字节的个人信息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分析和利用。奥巴马的助选团队甚至获取了有线电视公司的账单记录,来研究各个选民家庭收看了哪些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电视节目,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划分出各种各样的选民分组,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性价比向这些选民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政治广告推送。 [23]
正像在冲动的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微观定位手段的这种极度个性化的高效率特点反而让这项技术变成了民主过程和社区团结的摧毁者。从很多方面来看,传统的非个性化政治宣传运动在总体的政治过程中起到的是稳定与缓和矛盾的作用。在传统的竞选过程中,竞选者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尽量多的选民,因此他们必须选择更广泛包容的宣传平台,并且以各种手段把他们的政治立场包装得更加温和中立——虽然这些元素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低效率的元素,但这些元素使得传统的政治竞选过程能够起到稳定与缓和的效果。而微观定位技术却以最小化各种起缓和作用的低效率元素为目标,这种技术使得政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可以为每一类思维方式相近的选民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平台。因为有了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平台,候选人可以完全忽视“另一边”的选民。政治家所面临的压力减小了,他们不再需要发展出一个广阔包容性的平台,也不再需要表达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宏伟理念或者相对温和中立的政治信息。用竞选专家迈克尔·康的话来说,采用微观定位技术的政治竞选活动“完全不需要为了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把他们的立场做温和化或者中立化处理”。
除此之外,微观定位技术也降低了对选民的要求。事实上,微观定位技术可以被看作政治界的快餐。传统的大型市场竞选活动要求每一位选民都必须做出必要的努力:他们需要跨出自己狭窄的个人领域,需要走进混乱并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之中。而在微观定位技术的帮助下,今天的政治市场就像比萨饼和奈飞一样,能够方便地自动走向选民,而不需要选民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正像在消费者市场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技术使得政治与选民的自我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被微观定位的选民们不再需要做出智力和文明上的努力,不再需要对宏大的理念和复杂的概念进行分析,也不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协。事实上,以微观定位技术为标志的政治竞选活动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宏大理念的缺失。一位就职于纽约某家市场营销公司的竞选专家这样写道:“我们中的很多人将微观定位技术称为‘沉默的’市场营销。这是因为对于有效的微观定位营销活动而言,如果你在活动进行前和进行后两次对选民或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你会发现大部分选民或消费者并不记得他们听到过任何重大的、戏剧性的宣言,也不记得他们接受过打动他们的广告营销或任何形式的‘宏大理念’。这些选民或消费者只能回忆起这位竞选人或产品的哪些特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成功的微观定位技术是一种隐形的技术,它能够逃避所有雷达的侦测。” [24] 如今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市场营销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本质性的区别,政治越来越和消费者产品一样,变成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用来愚弄公众的工具。
微观定位技术的这种隐形特点对于参选的政客而言是一项非常明显的优点,因为你的对手根本无法看到你所发出的全部政治信息。然而,我们的政治过程本应是一种集体性的、公众性的、需要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因此这种隐形技术显然不利于我们的政治过程实现其正确的目的。参加竞选的政客可以使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微观主题来取悦所有可能支持他的选民,然而这样的行为却无法创造出一种单一的、强有力的、卓越的政治理念,而这种伟大的政治理念本应是政治家的一项最有力的武器。从前的政治家能利用这种武器在赢得选举后积极团结各部分选民,从而减小从选举到执政的过渡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阻力。然而在如今的政治模式下,选民们在竞选的过程中一直沉浸在一种高度个人化、充满狭隘情绪以及严重单边化的体验之中,因此在选举日结束之时,很多选民无法轻松地走出竞选模式——他们拒绝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继续前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妥协。换句话说,以前的选民可以坦然地相信,即便他们支持的竞选人输掉了选举,美国的政治体系仍然会有效率地运转,而今天的选民们似乎已经不再抱有这样的信念。如今,美国的公民们拒绝与和他们政见不同的人为邻,美国的议员们不再关注立法内容本身,而是一味地追求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未来的政治成功,并为此毫无原则的攻击和否认对手的所有观点和立场。当人们失去了妥协的精神和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人们就看不到任何将美国从这种可怕的政治文化中解脱出来的希望。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次政治竞选中,人们确实看到了上述不良气氛的盛行,不仅美国的选民们无法从竞选模式转换到执政模式,美国的立法者似乎也同样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协和联盟(一个试图游说政府缩小赤字规模的组织)的执行董事罗伯特·毕克斯比向我总结道:“两党都采取了同样恶劣的态度。两党都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与对方合作’。两党都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阻碍对方,我们就可以赢得下次大选,我们将在下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完成任何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它们的目的不再是政治和立法,而仅仅是获得选举的胜利。” [25] 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者经济体一样,我们的政治市场越来越执迷于对短期快速回报的追求,而越来越少地关注如何创造真正具有长期社会价值的产出。至此,我们的社会已经表现出了冲动的社会的终极症状:唯一可能拯救我们免于走向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制度,本身却已经被商业的蛮力所扭曲和重塑。 [26] 因此,这样的制度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避免这场战争,甚至还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永恒的战争。
然而,我应该记住的是,这场悲剧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人们的激情和异化倾向,而是我们的系统为了利用人们的激情和异化倾向而产生出的可怕动量和效率。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咨询师们会继续建议政党的候选人使用极端的政治战略,因为这种战略是这些咨询师取得胜利并赢得新客户的最高效的手段。问题的关键是媒体会继续发出违背本意的虚伪声音,因为它们不愿意承担损失受众份额的风险,不愿意放弃广告所带来的巨额收入。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政党已经对负面广告上了瘾,而这些负面广告会帮它们赢得更多的助选资金,这些资金又会被用来制造更多的负面广告。现在,这台巨大的机器已经完全控制了社会,甚至连这场游戏中的玩家们都已经开始感到紧张和焦虑了。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观察到共和党的领导人正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因为截至2010年,对共和党产生了巨大效用的保守派媒体突然之间变成了该党的一项巨大的债务和负担——这些媒体变成了一种由市场领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使得共和党无法关小虚比浮词的音量,无法采取一种更加实用的立法策略。2011年,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威胁要利用债务上限的谈判为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之后不久,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弗鲁姆写下了这样令人痛心的文字:“作为一种商业性的主张,这种模型(保守派的新闻产业)在奥巴马时代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从新闻的角度而言,这一模型却并没有带来什么良好的成果。而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这种模型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保守派的新闻渠道长期过分煽动观众,如今这些选民反过来迫使骑虎难下的共和党领导人不得不进行双输的无谓斗争。今年夏天由于债务上限问题而导致的政府关门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最佳例证。”然而,要想从这种尴尬而危险的情况中脱身是极为困难的。2010年,弗鲁姆在接受《晚间报道》节目的访问时这样说道:“共和党人曾经认为,福克斯新闻频道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而如今我们却发现,是我们在为福克斯新闻频道服务。这之间的平衡已经被完全反转了。让福克斯新闻频道长期保持强大的那些东西,恰恰是让共和党无法变得强大的东西。” [27]
美国的政党亲手建造的政治机器如今正以惊人的高效率运转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成员真的有意放弃这种令人着迷的高效机器。虽然最近出现了一些两党合作的意图和尝试,但似乎这场游戏的主要玩家以及手握操纵杆的重要人物们只不过是停下来充点电而已。在2012年被奥巴马团队用大数据技术击败以后,共和党为了在2014年的选举和2016年的大选中打出翻身仗,已经依靠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两兄弟的慷慨捐助投资了数千万美元来建立自己的大数据武器。当然,民主党也在拼命说服其金主来为更高效的政治技术埋单。2013年年末,华盛顿曾经举行过一次自由派捐款人的筹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已经退休的对冲基金大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宣布将拿出250万美元的现金作为助选资金。《纽约时报》认为,索罗斯此举是一种明显的信号,这种信号意味着美国的富裕阶级已经开始“提前为下一轮的大选做出承诺”了。 [28]
科赫和索罗斯等富豪的大名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冲动并不是最新的科技,也不是我们拒绝妥协的不良思维方式。事实上,真正的冲动是美国的政治机器所产生的可怕动量,这台机器已变得如此巨大、如此商业化,它极度依赖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从很多角度来看,这台机器更像是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一种政治体系。政治竞选的运行模式已经越来越像大型的高科技新创公司,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投资者”的大规模需求。两党之间进行着不断快速升级的“数据武器”竞赛,微观定位技术以及其他这方面的“武器”都是极为昂贵的,于是政治竞选成本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医疗成本的增长速度。2000—2012年,在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开支(以实际美元计)上升了三倍以上,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0亿美元。 [29] 国会竞选的成本也比过去上升了许多。在2012年,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成本是1 050万美元,而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则平均需要耗费170万美元, [30] 和1986年的情况相比,这两项成本都大约翻了一番。 [31] 2012年的所有选举活动总计耗费了63亿美元的巨资。 [32] 在这样的系统中,金钱已变得和选票一样重要,甚至已变得比选票更加重要。
不断上涨的金钱河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和锁定了冲动政治的各项特征。由于选举竞争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昂,在助选资金的资本市场上,赞助者们越来越不愿意在“挑战者”身上进行赌博,而更愿意支持已经持有席位的政客们。这种行为导致已经存在的两党对立结构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埃默里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花费在已经获得众议院席位的政客身上的助选资金(以及相应的捐款)增加了50% ,而花在挑战者身上的资金则减少了13%。 [33]
在更本质的层面上,由于政治活动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的政治经济必然越来越受金融化经济体的目标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控制。如今,筹集政治捐款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常年进行的经营活动——众议员平均每天要花费4小时的时间来给潜在的捐款者打电话。更严重的是,由于立法者必须筹集到大笔政治资金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倾向于那些能够提供大额支票的捐款者和商业板块,而这也意味着政治方向和议程必然会越来越符合这些大金主的利益。对于民主党的立法者而言,这尤其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从传统上来看,民主党一直致力于推进各种民粹主义的进程(比如劳工运动、环保主义以及少数人群的权益等),而如今却必须去取悦自己的资金基础——这一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仅不可能是民粹主义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根本与左派的进步主张相矛盾。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显示,比较富裕的选民通常更注重国家赤字削减、政府支出等政治问题,而不太关心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的赤字水平会影响央行制定的利率水平,而利率的波动对投资回报率有巨大的影响。研究显示,富裕人群中相信“联邦政府应把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的比例仅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3,而富裕人群中支持“联邦最低工资应该足够保证劳工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上”的比例仅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2。 [34] 前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佩列洛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说,民主党的主要资金捐助人“很可能认为政府赤字问题是比就业机会不足现象更严重的危机”。 [35] 佩列洛认为,由于这些为美国进步的左派中心提供资金支持的捐款人的优先目标发生了变化,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被注入了“一个巨大的反民粹主义元素”。 [36]
经济学家迪安·贝克是经济政治研究自由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也表达了与佩列洛相似的担忧。贝克说:“那些为政治竞选活动埋单的人现在状态好得不得了。这些人是那些手头持有大笔现金的人,是公司的高层。他们已经完全从上次的经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美国的股市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公司利润也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根本不觉得失业现象是一个大问题。”贝克认为,这样的现状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提议采取政府行动解决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那么它们很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大赞助商的支持。贝克说:“如果你跑去找一位赞助商并对他说:‘你看,我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刺激我们的经济,能把失业率降低2~3个百分点。’那么对方一定会说:‘我们干吗要那样做呢?你这么做只会加大政府的赤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坐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经济自动好转呢?’” [37] 在如今资本密集型的政治产业中,民粹主义早已变成了一种需要被从政治机器中挤出去的低效率元素。
事实上,由于政治竞选活动对资金的要求不断高速增长,整个政治文化已经不再有空间去容纳和回应那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曾经极力拥护的重要问题了。如今,金融板块是政治竞选活动的最大赞助商之一,金融板块有着巨大的利润盈余,并且在最近几年中,它们有极强的动机要把这些利润盈余中的一部分花在华盛顿的政治活动中。1992—2012年,金融板块对竞选活动的注资数额(以实际美元计)几乎翻了七番,达到了6.65亿美元, [38] 在对政治竞选活动的注资规模上,金融板块超过了其他任何板块, [39] 1992年,金融板块的注资只占整体竞选支出的4%;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1.5%。 [40] 此外,仅在2012年一年,金融板块就花费了近5亿美元的巨资用来游说政府的立法者和管理者们。 [41]
金融板块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最能看到这种公开影响力的地方恐怕要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对华尔街实施监管,而来自金融板块的大量竞选赞助资金几乎每天像暴雨一样浇在该委员会委员们的头上。由于这个“现金委员会”的席位是如此的值钱,自1981年以来,该委员会总共增加了17个新席位,总委员席位数量达到了61个。 [42] 一旦一名众议员首次赢得了该委员会的席位,金融行业的说客就会以职业体育俱乐部挑选大学生运动员那样的热情对这名新委员进行最详细的审查。在一篇关于这个“现金委员会”的杂志报道中,记载了一位说客与《时代周刊》的埃里克·利普顿的对话。 [43] 这位说客表示:“这个过程很像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或者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中俱乐部对第一轮获选新秀进行的投资。我们看到了这里存在的潜力,因此我们愿意进行投资,我们希望这样的投资日后能够产生回报。”在大部分情况下,华尔街对这些投资的回报感到相当满意。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国会的其他部分,甚至整个白宫都充分照顾了华尔街的利益。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承诺进行的很多改革措施都因此被严重弱化甚至完全消除了。
华尔街从来都把华盛顿视为一项可以产生巨额回报的投资财产。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国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说,国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曾对金融板块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措施,政府的政策甚至常常对金融板块抱有一定的敌意,然而如今,政府对金融板块的态度变得友善了许多。虽然这种对金融更加友善的新态度始于共和党人尼克松和里根执政的时代,然而如今金融板块的最大政治支持者却常常是民主党人。事实上,正是民主党人在20世纪90年代把金融板块从大萧条后的严厉管制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民主党人应对金融板块的自由化过程负有最大的责任。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曾禁止商业银行同时在金融市场开展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推翻,而领导推翻该法案的政治运动的头号功臣正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高盛的前任老板罗伯特·鲁宾。罗伯特·鲁宾还帮助华尔街击退了试图对CDS(信贷违约掉期)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实施监管的政治力量。这两项去管制化的政策为华尔街开辟了收入和利润的新来源,而这些巨额的利润又成为民主党助选资本的一个巨大的新来源。然而,这两项政策同时也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由于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行为,而在这些不受政府管制的金融衍生品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亏损几乎完全摧毁了当时的全球金融系统。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巨大悲剧,民主党和华尔街之间的联盟关系却依然稳固。虽然奥巴马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医疗改革方面)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些非常激进的改革努力,然而他在金融方面的立场却是非常老派的。虽然奥巴马在2008年的大选过程中曾对华尔街做出过极为严厉的批评,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却很快建立了与金融板块的联系,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举动是奥巴马任命了罗伯特·鲁宾的追随者——蒂莫西·盖特纳作为他的财政部部长。虽然我们应该承认,盖特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危机的继续恶化,但盖特纳也从未放弃对华尔街尽忠的目标。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华尔街的银行规模过于巨大,因此它们的投资行为已经造成了对整个美国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基于这样的考虑,出现了拆分华尔街银行的提案,很多金融专家认为,这样的提案完全可能促成一次根本性的金融改革。然而,在盖特纳的努力下,这样的法案以及很多其他不利于华尔街的法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此外,对于在本次危机中起重要作用的华尔街机构,奥巴马政府也放弃了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虽然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些机构涉嫌欺诈。最终,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再次复苏的各种过剩现象坐视不管,这些过剩的现象包括巨额的工资和奖金,以及投资者的短视思维对公司策略所起到的严重的腐蚀性影响。至此,我们见证了冲动的社会的又一次胜利:强有力的金融板块将美国的政治文化转化为暴利的保护伞,这些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暴利又被再次投资于政治领域,用来制造新的寻租机会。
可悲的是,唯一能阻止美国的政治文化不被完全金融化的公共制度——法庭最近也沦陷了。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针对公司向政治活动委员会进行政治捐助的一切限制。此次判决生效后,政治活动委员会可以使用这些资金来发布支持和攻击任何候选人的广告(大部分广告是攻击对方候选人的广告)。在这次判决生效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靠公司资金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一举筹得了3亿美元的资金。 [44] 而到了2012年大选时,上述金额又翻了一番。
联合公民诉讼案向我们展示了金融市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穿透和控制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做出这次判决后,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表示:这次判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良性的。肯尼迪大法官的这种看法恐怕只有那些被隔离在华盛顿的小世界中的人才会同意。肯尼迪大法官认为,虽然这样的判决结果使得公司能够对美国的政治过程“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或介入”,但他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会让选民丧失对我们的民主制度的信心”。 [45] 肯尼迪大法官的这种看法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向政治竞选活动捐献资金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表达个人看法的权利。这一论调常常被公司律师用来作为支持一项范围更大的法律运动的论据,这项运动希望法律能保证公司享有与个体公民完全相同的权利——如果这样的运动获得成功,那么公司在事实上就能够通过金钱购买其所希望的任何政治结果,这样的行为与冲动的社会中个体消费者用金钱购买即时满足的行为确实是高度相似的。然而,这样的论点也触怒了很多不是公司律师也不是政治说客的美国公民,尤其是那些个人生活被美国公司的这种追求自我满足的浪潮严重损毁的公民。
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成因便是公司的这种狭隘自我对短期回报的过度追求(并在亏损后不知羞耻地要求政府用公共资金对它们进行救援)。然而就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便出现了联合公民诉讼案的判决结果,这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很多普通的美国公民来说,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似乎已经成为金融板块的帮凶,或者说成为金融板块的一种延伸。现在,美国的政治体系的行为模式已经与市场完全一致,美国的政治体系有着与市场一样的短视,与市场一样的“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政治体系与市场一样把狭隘的个人利益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与市场一样重视资产而轻视个人。 [46]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家政治似乎回到了大量进步改革措施实施之前那种野蛮而又腐败的世界中。罗斯福以及威廉姆·塔夫脱等进步派改革人士的努力似乎已被完全抹去。在改革之前的黑暗日子里,国会议员席位可以被公开购买,公共资金可以被随意掠夺,而普通的美国公民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政治家当作为富裕阶级谋取利益的垫脚石。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难怪一些严肃而愤怒的民粹主义运动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09年的茶党运动出现之后,在两年后又出现了更严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当愤怒的示威者们占领了纽约市曼哈顿的祖科蒂公园,对腐败的金融系统以及同样腐败的政治体系进行抗议时,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深感惊讶。让人们惊讶的并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抗议活动,而是这样的抗议行为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发生。
那么,这样的愤怒情绪为什么没有转化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呢?美国的这种新型的金融化的、高效率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的政治世界必然导致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比如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崩溃、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国家立法程序的瘫痪。按理说没有比这更容易促成长期的示威反对运动的情形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反对运动主要针对相关问题的表面,而未能直指问题的核心。“占领华尔街”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引起实体经济界的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另一项示威运动——茶党运动——倒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茶党运动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阻止政府采取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来对上述不平衡现象进行修正,这种方向完全错误的抗议运动反而高效地取得了成果。茶党运动事实上控制了整个共和党,并最终让后者成功地关停了美国政府。可悲的是,当美国的政治文化不再追求真正的政治变革,而主要追求品牌效应和自我身份的创造时,茶党运动的这种荒谬的结果正是人们唯一可能得到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派人士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虽然“占领华尔街”反映出了主流自由派人士对华尔街及其走狗——政府的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及对根本性改革措施的呼唤,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却未能成功地唤起很多主流自由派人士的热情。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占领华尔街”根本没有为争取主流的支持做出足够的努力。相反,发起“占领华尔街”的主要群体既不愿意与媒体沟通,也不想和潜在的同盟者(比如广大劳工阶级)进行合作。这一抗议群体也同样不愿意提出,同时也没有能力提出一套合理的改革方向和方案。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占领华尔街”的参与者仅仅是想发泄一种冲动的政治愤怒,这场运动完全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构和过程,因此注定不可能成为一场主流的运动。用本书中的话来说,“占领华尔街”更多地来自“短视的冲动者”,而不是来自“长远的计划者”。
然而,就算“占领华尔街”能被组织得更加“专业”一些,我们也无法确定主流自由派人士是否愿意加入这场高风险的集体性抗议活动,这些活动的地点主要在祖科蒂公园以及美国数百所其他公共场所。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左派人士与集体活动或者说“集体性”的概念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十分尴尬的关系。反主流文化的冲动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如此的强烈,以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风潮已经被主流消费者文化所吸收,而主流消费者文化的重要特征便是它随时准备将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转化成一种商品或服务。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激进的反主流文化人士甚至已经变成了消费者文化的代言人:艾伦·金斯伯格代言了Gap(盖璞)牛仔裤,而威廉·巴勒斯则开始宣传耐克公司的AirMax系列产品。而对于我们中的其他人而言,示威和抗议变成了一种方便的商业化消费品,身在消费者经济体中的我们只要走进商场,便可以轻松地获得为个人自由而斗争的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的新左翼群体(那些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愿意为了争取民权或抗议越南战争而走上街头示威的男男女女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的中产阶级所同化。物质的理想代替了政治的理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自由派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为了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所采取的保守派政策而走上街头。然而,仅仅20年后,当里根政府再次推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时,同一批自由派人士已经不再愿意走上街头,而选择搬去看不到支持里根的条幅的社区中居住。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再要求选民走出自己的狭隘个人利益,去拥抱某种更广阔的国家目标。对于很多“婴儿潮”一代的人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身份确认的工具,只有当政治适应我们的日程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只有当我们需要填补内心的空虚时,我们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对这一代人而言,政治再也不是一种要求人们忍受不适、延迟满足、做出艰难选择的东西了,因此也再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了政治而忍受催泪弹的攻击。
当然,这些逐渐老去的左派人士并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对一个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的渴望。只要看一下Daily Kos等网站的流行程度,我们便会发现美国仍然存在着一个规模很大的关注政治的左派群体。然而,Daily Kos等网站也同时完美地展现了人们的政治理想在冲动的社会的环境中发生了怎样的进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退化)。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椅自由派”的国家,我们只愿意坐在安全舒适的客厅里或者办公桌前,对美国的政治问题品头论足、指手画脚。想要鼓励伊丽莎白·沃伦竞选总统吗?请点击这里。想要告诉哈里·里德他应该停止使用冗长的辩论来阻碍法案通过吗?请点击这里。想要支持“占领华尔街”吗?请点击这里。然而要想让我们真正走上街头,忍受种种不适,面对“占领华尔街”人士所面临的那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风险(顺便问一句,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种程度的白人对白人的警察暴力了)? [47] 不好意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想承受这样的风险。因为我们高度工业化、高度金融化以及高度商业化的政治文化早已不再鼓励人们承担这样的风险了。
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已经不再存在一个有效的左派群体了。至少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如20世纪30年代劳工运动高峰时或者战后时段末期抗议运动盛行时的那种积极的、强大的左派力量了。政治分析师皮特·贝纳特认为,这样的情况对美国的政治过程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样的情况致使民主党人放弃了很多曾经是该党核心理念的东西。贝纳特还认为,由于美国缺乏有力的左翼群体,由于不再有政治积极分子愿意走上街头打破美国的政治现状,如今的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与保守派协商的筹码。贝纳特这样写道:“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林登·约翰逊不同,克林顿或者奥巴马永远无法真正有效地威胁到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因为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们不通过自由派的改革法案,左翼激进分子就可能做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与此同时,左翼力量的缺失使得今天的民主党能够轻松地采取很多以前只属于右派的行为,比如大规模地从公司赞助商处获得助选资金,以及对华尔街采取高度友好的态度。贝内特写道:“今天的民主党人发现,与保守派世界的大公司和大财团建立关系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已经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左派运动来对民主党的上述行为施加反对压力了。” [48]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左派所采取的这种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主张直接导致了金融去管制化政策的出台,也继而促成了后续危机的发生和发酵。由于今天的美国左派高度关注自我表达和对个人成就的追求,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该派力量的历史功能:对政府起制约作用,保证政府不能彻底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盲目地追求效率的提高。
然而,右派的茶党却完全不存在左派的这种缺乏支持基础的问题。自茶党诞生之日起,这场右派的革命就得到了保守派政治机器的热烈肯定。而这台右派的政治机器与左派相比,不仅行动能力更强,资金基础也更为雄厚。当“占领华尔街”人士拒绝与媒体进行沟通时,很多茶党的积极分子却接受过极为专业的媒体管理训练。右派的各种集会和政治活动不仅经过精心的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集会和活动受到了媒体和当地立法者的支持和配合。茶党不仅邀请当地的立法者参与这些活动,并且还警告这些政客:如果他们不支持茶党的政治主张,就会在下一次的初选中面临严重的麻烦。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茶党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不如占领祖科蒂公园的群众的愤怒情绪真诚,我也并不是想说茶党完全是由右翼说客和百万富翁们创造和控制的。在茶党运动的中心,以及在更广泛的红色州的“品牌标志”中心,确实存在着一种深刻而真实的焦虑情绪,是家庭、社区、自力更生精神等重要社会价值的逐渐消失导致的。当然,在茶党的世界中,对这些传统价值观的珍视中还混杂着其他一些没有那么高级的情绪,比如偏执和顽固。此外,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利用,成为他们操纵选民的工具。事实上,尼克松就曾经成功地挖掘和利用“沉默的大多数”的焦虑情绪,从而获得了连任选举的胜利。可见,利用传统价值观来操纵选民早就已经是共和党人的传统。然而,尼克松和他的保守派后人(比如里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战后的自由商业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确确实实地引起了很多美国人(不仅仅是狂热的保守派、自由派、生存主义者 [49] )的不满。
从保守派的角度来看,积极干预商业活动的大政府以及过于广阔的社会安全网不仅掏空了美国的国库,而且制造了一群新型的、令人讨厌的美国公民:他们愚蠢而又以自我为中心,心安理得地把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和权利当作他们理所应得的东西;他们完全看不到物质世界的现实情况,也毫不尊重长期保持美国社会活力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保守派的这些看法并不仅仅针对那些整天吸大麻的嬉皮士以及靠福利生活的社会寄生虫。事实上,这种情绪反映出的是一种更为深刻和真诚的恐惧情绪——他们担心美国公民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和支持美国的传统社会制度和规则。而在这些保守派人士的心目中,这些社会制度和规则正是促成美国稳定、高产、快乐的优良文化的核心因素。对此,保守派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和警告:这些新型的自由派公民“不仅拒绝美国的过去,也否认他们与社区的关系。美国要生存下去,就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鄙的返祖现象,不能让这种新型的野蛮主义继续存在下去”。 [50] 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仿佛发现了莱格英哈特所描绘的超物质主义人群的阴暗面,就像美国社会的衰退完全是这群人的自私和短视所致。
虽然上述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但保守派对上述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杰瑞·法威尔等社会保守派人士提出的虔诚的、道德圣战式的解决方案被大多数主流选民认为是陈旧的、脱离现实的。而问题更严重的是里根及其他自封的“财政保守派”人士所提出的经济方针:向美国经济中注入大剂量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猛药,却完全不以政府监管和制度对此进行限制和规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保守派所实施的这些政策最终只会让他们想要保存的这些社会价值被更快地侵蚀掉。虽然这种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撕裂了美国的社会,拖垮了劳动力市场,加速了收入不平均现象的升级,使得家庭、社区以及本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们的生活变得极为困难,然而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却让他们继续无视现实的矛盾,继续无视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或者牵强地声称这些成本都是社会前进的自然规律。如果说左派的问题是常常过度怀疑市场的力量,那么如今的保守派则显然过度迷信市场的力量了。在里根经济革命的最高峰,保守派的社会批评家理查德·约翰·纽豪斯和皮特·伯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经常表现出与左派完全相反的弱点:他们对大政府的异化过度敏感,却对大公司的同样行为视而不见”。而就职于保守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勒特韦克则进一步指出:保守派的这种盲点“导致主流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刺眼的巨大矛盾”。 [51]
为什么保守派人士如此不愿意正视市场的这种分化和腐蚀的力量呢?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惧。平心而论,保守派的这种恐惧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因为政府试图控制经济的种种努力几乎总是会创造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就对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要真正理解右派对自由市场悖论的盲目否认态度,我们就必须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政治品牌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过去的20年中,政党、咨询师以及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已经成功地将个人对政治的参与活动转化成了一种与消费产品高度相似的东西——通过参与政治活动,选民可以满足自己的热情与幻想,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也不需要经历任何形式的不适,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协。然而,虽然这种品牌包装的效应确实在近些年来为政党(特别是保守派政党)带来了短期的政治回报,但这一过程也同时导致美国的政治文化几乎失去了推进政策或者做出重要抉择的能力。比如,在目前保守派政治品牌的理念中,妥协的理念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因为在这种品牌理念中,妥协行为与保守派“正统”的自我身份定位在道德上是不相融的。因此,不管是保守派的选民还是保守派的政治领袖,都认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无处可去,只能从相对中立的立场不断向极右主义和极端主义移动。
然而,保守派的品牌形象中的这种矛盾的元素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比如,由于自由市场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如今的保守派已经越来越难以同时坚持以下的两种信念:一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二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对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负责。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中,劳动者即使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来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状态,也很可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右翼品牌已经逐渐失去了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民意基础。在里根的时代中,由于自由派的罗斯福新政方针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病(比如大社会项目的垮塌,以及许多工会中存在的腐败与自满现象),保守派的主张能够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然而如今的保守派品牌在现实中的根基已变得越来越不稳。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灾难与经济问题,以现实为基础的保守派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奉为神谕的自由金融市场的智慧。
然而,由于右翼的品牌形象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很多保守派人士甚至拒绝考虑效率市场有可能失灵的可能性。一些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很多将自己定义为保守派的人士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主要应该归罪于政府支持的房屋贷款,同时他们认为工作岗位数量回升过于缓慢的现象是政府的过度管制造成的。而这些人绝对不肯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效率市场本身也许已经出现了腐化的现象和巨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也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守派的品牌形象已经被现实磨损得差不多了。因为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比较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尤其是近期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年轻人)远不及老一辈人那么迷信市场的力量,也相对较能接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然而,品牌化的保守主义已经完全控制了共和党的整个系统(这尤其体现在对初选候选人的选择上),因此它们的品牌理念只能向更极端的方向越走越远。
这样的情况导致共和党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经济问题提出实质性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共和党议员都相信,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制度不仅导致百万富翁所面对的税率比挣工资的中产阶级劳动者面对的税率还要低,而且这样的税务制度还允许股票持有者不断买卖手中的股份,却几乎不会受到什么税务方面的惩罚,这一制度因此鼓励了市场上的一些最为糟糕的短视行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文化中,对资本利得的征税方法应该能够鼓励投资者长时间持有股票(连续持有5年或更长的时间)。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达蒙·西沃尔是一位研究商业短视问题的专家,西沃尔曾这样说道:“我知道共和党中其实有很多比较中立的立法者,他们非常愿意考虑对资本利得税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并支持上调针对短期交易产生的资本所得的税率。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可以实行的。然而,现在阻碍这一改革措施实施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商业界的阻力,而是茶党的反对。因为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提高税率,茶党就一定会以最坚决的态度表示反对。因为事实上,茶党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阻止政府提高税率。”
政治文化是一头难以驯服的复杂猛兽,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正导致左派和右派意见分歧的鸿沟日益加宽。比如说,大量行为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对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危机所做出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相较于自由派人士而言,保守派人士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让个人独自承担经济困难的重担。同时还有一些研究的结果显示,保守派人士更加不愿意挑战权威,因为挑战权威的行为会给他们造成更强的不适感。这种不愿挑战权威的心理特点导致保守派人士更难以支持任何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而想要深刻地改变美国目前的政治现状,就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然而,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分析和梳理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保守派对于明明已经严重腐化的商业市场的那种奇怪的忠诚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加本质的心理动因,那就是我们高度工业化、高度个人化、具有超高效率、靠人们的自我驱动的冲动政治文化已经重新塑造了保守派人士的自我身份定位。为了维护这样的自我定位,保守派人士不再能承认任何妥协的必要性,在他们的字典里,妥协这个概念已经被完全删除。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自由派的政治机器也同样受到了这种身份塑造政治的污染,同时现代的政治文化本身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受害者文化”意识形态的腐蚀。 [52] 然而在这一方面,右派的问题显然比左派严重得多。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表明,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从中立立场向右移动的速度更快,同时保守派人士的立场也比自由派人士更加顽固和难以改变。也许,这只是因为现代化的世界狂热地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严重弱化了社区概念及其稳定性。也许右派的过激行为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了太深的恐惧和失望。然而,不管右派的这种趋势成因究竟为何,这种趋势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传统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已经逐渐丧失了神圣的光环,但是对于今天的保守派人士而言,他们离能够勇敢地正视这一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一天不完成这样的挑战,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就无法真正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所带来的难题与困境: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体正越来越严重地强调和鼓励对即时满足和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而社区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思考则越来越被美国社会所抛弃。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怀疑美国的政治体系,耐心和希望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比如说,虽然年轻的美国人向来不愿意积极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但如今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的潜质和迹象。很多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千禧一代 [53] 的年轻人不像老年人那样乐于参加投票,但他们更倾向于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通常更愿意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融入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是把参与政治当作一种仅在大选时发生的行为。此外,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也不像较年长的美国公民那样喜欢上文我们所提到的那种品牌化的政治理念。比如说,千禧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辈的保守派更能够包容种族方面的多样性,同样的,他们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度也比老一辈保守派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千禧年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代保守派更能够质疑大型商业公司的行为,并且他们将政府视作一种能够修正经济方面的不平衡现象的潜在有益力量——新一代保守派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美国商业界最为腐败的时段。皮特·贝纳特等政治观察家认为,不管是哪个政党或政党的政治领袖,只要他们能向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传递正确的政治和经济信息,就能够在选举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支持集团(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党极力争取伊丽莎白·沃伦,因为她被视作争取千禧年一代保守派青年的理想竞选人)。而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根本性改革给予更多的重视。 [54]
然而,一项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个新的选举支持集团很可能并不能用传统的左翼、右翼或者保守派、自由派的方法来予以归类。事实上,在经历了持续若干年的两党纷争和品牌政治以后,我们很可能即将看到一个新的中立选民群体的产生。最近的一些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量的选民虽然分属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的不同阵营,但他们对一系列内容宽泛的政治议题实际上却有着高度统一的态度,这些政治议题包括妇女堕胎权、贩售枪支的背景调查、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宗教和国家的分离问题等。《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中立偏右的专栏作家凯瑟琳·帕克曾这样写道:“这些人的共同点远比各种相左的极端意见更多,而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对‘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纯粹’这一理念的反对。” [55] 显然,这一选民集团已经在2012年的大选中展示了他们的存在及其潜在力量。在2012年的大选中,选民对茶党极端主义的反对是共和党最终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立派的美国人并不仅仅是反对极右势力所倡导的不平衡的政治理念。他们同时也支持更传统的、更平衡的美国式政治理念。《华盛顿邮报》的自由派专栏作家、《我们分裂的政治之心》一书的作者小尤金·约瑟夫·迪昂曾说,2012年的大选实质上反映了选民对美国战后时期平衡政治理念的认同与支持,这种理念“包括自由主义与社区之间的平衡、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市场功能与政府的重要角色之间的平衡,在清理长期的自由市场主义留给我们的各种问题时,掌握这些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56]
保守派的政客也许并不会使用和小尤金·约瑟夫·迪昂完全一样的说法。但是在2012年的大选失败之后,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共和党的主流至少已经做好了放弃极端主义、将共和党的品牌形象重新向中立方向移动的准备。2013年年末共和党对茶党所采取的谴责态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这一信号说明,即使是在华盛顿的封闭政治王国中(这可能是整个美国社会中分类现象最为严重的社区环境),人们也已经意识到维持现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犬儒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茶党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失去了商业集团(尤其是金融板块)的支持,商业集团和金融板块担心茶党的极端主义作风会降低共和党抢占管理改革先机的能力。但是,共和党对茶党的谴责态度也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文化终于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显然,美国的选民们已经受够了长达几十年的党派政治战争。平心而论,甚至很多强调意识形态的立法者们也因为茶党起义的最终失败而松了一口气。在一个非常基础的、人性化的层面上,政府关闭的闹剧为斗争中的双方都提供了一个他们急需的暂停时间。在经历了几个月中不断升级的野蛮两党斗争以后,双方的立法者们终于可以各退一步。即便这样的妥协与和解是暂时的,这一现象也至少让快要把美国的政治文化推下悬崖的那台永不停息的跑步机暂停了一会儿。在这种来之不易的开放性空间中,两党的立法者终于成功达成了一些虽然微小却十分重要的妥协法案。当然,没有人相信这种和平的景象会长时间持续。显然这台制造冲突的机器只是暂时停下来充电,为2014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而已。然而,即便是这种短暂的和平也足够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最需要的,是双方各退一步,远离这台危险的政治机器,为双方都创造一些呼吸的空间。我需要这种呼吸的空间去反思、去权衡、去选择一条能做出实际行动的道路,而不是仅仅让这台政治机器的惯性驱动我们的决策、战略以及命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短暂的和平之中,似乎冲动的社会的首都华盛顿正向我们展示着,一个解除斗争武器装备的社会本来应该是多么的宁静与美好。
[1] 关于这次晚餐会议的情况最先是由汤姆·贝文和卡尔·坎农在他们2011年所出版的书籍《2012年大选:斗争开始了》中披露的。几个月之后,罗伯特·德雷珀在《不要问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一书中进一步披露了此次会议的详情。
[2] Sam Stein, “Robert Draper Book: GOP Anti-Obama Campaign Started Night of Inaugura tion,”Huffington Post , April 25, 2012, http://www.huf f ingtonpost.com/2012/04/25/robert draper-anti-obama-campaign_n_1452899.html.
[3] Ibid.
[4] Ibid..
[5] “言论摘要”,指从政客长篇讲话中截取的、能快速打动选民的金句。——译者注
[6] “Vote Tallies for Passage of Medicare in 1965,” Of f icial Social Security Website, http://www.ssa.gov/history/tally65.html.
[7] Alan Abramowitz, “Don’t Blame Primary Voters for Polarization,”The Forum: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Selection 5, no. 4 (2008), http://www.themonkeycage.org/wp-content/uploads/2008/01/Abramowitz.Primary.Voters.pdf.
[8] David Schoetz, “David Frum on GOP: Now We Work for Fox,” ABCNews, March23,2010, http://abcnews.go.com/blogs/headlines/2010/03/david-frum-on-gop-now-we-work for-fox/.
[9] “Q3 2013 Cable News Ratings: Fox #1 Overall, MSNBC #2 in Primetime, CNN #2 in Total Day,”Mediate , Oct. 2, 2013, http://www.mediaite.com/tv/q3-2013-cable-news ratings-fox-1-overall-msnbc-2-in-primetime-cnn-2-in-total-day/.
[10]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在两极化的政治新闻环境中,占最大份额的电台谈话节目之所以能够诞生,是因为在里根时代美国政府对无线电波领域推行了去管制化的政策。在此之前,大萧条时代的公平主义政策要求所有广播节目频道将节目时间平均分配给民主党和共和党。
[11] 一项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相对中立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目前正面临着黄金时段观众数量下降的挑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在目前的新媒体市场上,“如果一个新闻频道既不愿意公开表现自己对自由派的支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自己对保守派的支持,那么这个频道就注定会在收视率的战争中处于劣势”。
[12] Abramowitz, “Don’t Blame Primary Voters for Polarization.”
[13] “Polarized or Sorted? Just What’s Wrong with Our Politics, Anyway?”American Interest ,March 11, 2013,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393.
[14]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15] Kevin Drum, “You Hate Me, Now with a Colorful Chart!”Mother Jones , Sept 26,2012,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2/09/you-hate-me-now-colorful-chart.
[16] 蒙太古和凯普莱特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势同水火的两个家族。——译者注
[17] 通过冗长的辩论来阻挠对方通过法案或达到其他政治目的是美国政治中的一种议事策略,通常占劣势的一方会通过马拉松式的演讲来让议事过程瘫痪,迫使对方让步。这种策略英文叫作“fi libuster”,又译作“拉布”。——译者注
[18] “动员选票”活动,指在选举当日各政党会利用一切手段——比如登门拜访、邮件、电话以及为选民提供交通工具等方式——来鼓励支持自己的选民去投票现场投票。——译者注
[19] Steven Pearlstein, “Turned off from Politics? That’s Exactly What the Politicians Want,”The Washington Post , April 20, 2012, http://www.washing tonpost.com/opinions/turned off-from-politics-thats-exactly-what-the-politicians-want/2012/04/20/gIQAffxKWT_story.html.
[20] 一位参加过2004年布什竞选工作的官员在布什获得二次竞选胜利后曾这样夸耀道:“我们发展出了一套与美国公司每日所使用的消费者模型完全一样的模型,我们可以借此精确地预测出选民的投票行为——不仅仅基于他们居住的物理地点,还根据与他们生活方式相关的各种数据。”
[21] Alex C. Madrigal, “When the Nerds Go Marching In,”The Atlantic , Nov. 16,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2/11/when-the-nerds-go-marching-in/265325/?single_page=true.
[22] Michael Scherer, “How Obama’s Data Crunchers Helped Him Win,”Time , Nov. 8, 2012,http://www.cnn.com/2012/11/07/tech/web/obama-campaign-tech-team/index.html.
[23] Madrigal, “When Nerds Go Marching In.”
[24] Tom Agan, “Silent Marketing: Micro-Targeting,” a Penn, Schoen, and Berland Associates White Paper, http://www.wpp.com/wpp/marketing/reportsstudies/silentmarketing/.
[25] Interview with author.
[26] 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自然状态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希望占有世界上的所有资源,而人们所拥有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因此,这种争夺权力的斗争会演化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霍布斯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以及短暂的”。——译者注
[27] Schoetz, “David Frum on GOP.”
[28] Nicholas Confessore, “Groups Mobilize to Aid Democrats in ’14 Data Arms Race,”New York Times , http://www.nytimes.com/2013/11/15/us/politics/groups-mobilize-to-aid democrats.html?hp=&adxnnl=1&adxnnlx=1384974279-yMZXrvK1b5WLU7mXxrJ6yg.
[29] “Data Point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pending,”U.S. News & World Report , http://www.usnews.com/opinion/articles/2008/10/21/data-points-presidential-campaign-spending.
[30] David Knowles, “U.S. Senate Seat Now Costs $10.5 Million to Win, on Average, while U.S. House Seat Costs $1.7 Million New Analysis of FEC Data Shows,” (New York) Daily News ,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politics/cost-u-s-senate-seat-10-5million-article-1.1285491.
[31] “The Cost of Winning an Election, 1986–2012,” table, http://www.cf inst.org/pdf/vital/VitalStats_t1.pdf.
[32] “The Money behind the Elections,” OpenSecrets, http://www.opensecrets.org/bigpicture/.
[33] Alan Abramowitz, Brad Alexander, and Matthew Gunning, “Incumbency, Redistricting,and 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 in U.S. House Elections,”Journal of Politics 68, no. 1(Feb. 2006): 75–88, http://www.stat.columbia.edu/~gelman/stuff_for_blog/JOParticle.pdf.
[34] Cited in A. Lioz,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 How the Supreme Court Helped Create the Inequality Era and Why a New Jurisprudence Must Lead Us Out,”Seton Hall Law Review 43, no. 4, Symposium: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Election Law, Nov 1, 2013.
[35] Sabrina Siddiqui, “Call Time for Congress Shows How Fundraising Dominates Bleak Work Life,”Huffington Post , Jan. 8, 2013, http://www.huffi ngtonpost.com/2013/01/08/call-time-congressional-fundraising_n_2427291.html.
[36] “Tom Perriello: President & CEO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Counselor to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taff bio, http:// www.americanprogress.org/about/staff/perriello-tom/bio/.
[37] Interview with author.
[38] “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 Long-Term Contribution Funds,” graph, http://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totals.php?cycle=2014&ind=F.
[39] “Ideology/Single-Issue: Long-Term Contribution Trends,” graph, OpenSecrets, http://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totals.php?cycle= 2014&ind=Q.
[40] Patrick Basham, “It’s the Spending, Stupid! Understanding Campaign Finance in the Big-Government Era,” Cato Institute Brief ing Paper No. 64, July 18, 2001, http://www.cato.org/sites/cato.org/f iles/pubs/pdf/bp64.pdf.
[41] “Ranked Sectors,” table, OpenSecrets, 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showYear=2012&indexType=c.
[42] Eric Lipton, “For Freshman in the House, Seats of Plenty,”New York Times , Aug. 10,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8/11/us/politics/for-freshmen-in-the-house-seats of-plenty.html.
[43] Ibid.
[44] Jeffrey Rosen, “Citizens United v. FEC Decision Proves Justice Is Blind — Politically,”The New York Times , Jan. 25, 2012, ht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0112/71961.html.
[45] Ibid.
[46]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完全不应该感到惊讶。毕竟在美国的参议员中,每3位议员有2位的个人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而在众议院中,每5位议员有2位的个人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
[47] 美国的大部分警察暴力事件受害者都是少数派族群,比如黑人。因此作者认为警察对于“占领华尔街”的群众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十分耐人寻味。——译者注
[48] Peter Beinart, “The Rise of the New New Left,”The Daily Beast , Sept. 12, 2013,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9/12/the-rise-of-the-new-new-left.html.
[49] 生存主义者是一群以最大化个人或群体在危机中的生存概率为信念的人,他们通常很重视对经济危机、金融灾难等危机状况的预防和准备。——译者注
[50] “Man and Woman of the Year: The Middle Americans,”Time , Jan. 5, 1970, http://www.time.com/time/subscriber/printout/0,8816,943113,00.html.
[51] Clifford Cobb, Ted Halstead, and Jonathan Rowe, “If the GDP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The Atlantic , Oct. 1995,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politics/ecbig/gdp.htm.
[52] 但是显然右翼的思想家们过度夸大了这种腐蚀和污染的程度。
[53] 千禧一代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生,21世纪进入成人期的一代。——译者注
[54] Beinart, “The Rise of the New Left.
[55] Kathleen Parker, “A Brave New Centrist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 , Oct 15, 210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kathleen-parker-a-brave-new-centrist world/2013/10/15/ea5f5bc6-35c9-11e3-be86-6aeaa439845b_story.html.
[56] E. J. Dionne, Our Divided Political Heart: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Idea in an Age of Discontent :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 p. 270.

在某些层面,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某些社区中,不管是一周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经常是拼命地)试图在自己和将效率与高速回报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寻求一点空间。这可以表现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们决定能有一天远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的控制,重新获得一些家庭的亲密氛围。或者超负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向上司请假,为的是能与上幼儿园的孩子共度温馨的亲子时光。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某位女士决定停止网购和使用信用卡,因为她再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第三方营销公司或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所窃取。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可以表现为热衷政治新闻的网民最终决定戒掉福克斯新闻频道或者Daily Kos网站,因为这些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摧毁他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当然,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像本书开头提到的布雷特·沃克那样,下定决心让自己脱离数字世界的控制。这些反叛者也许从未对冲动的社会正式宣战,但这些反叛行为随处都在发生,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无人驾驶的巨型跑步机一样,如果不能让自我与这台机器的惯性、预期和价值观保持适当距离的话,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东西。
我们对美国社会的这些反叛行为源自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同时也来自信仰的丧失。在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以后,很多美国人已经不再信任冲动的美国的基本结构及其隐含的一些假设。不但我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经济体系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彻底腐蚀,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业界的冷酷与野蛮以及周期性的市场崩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现实。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其他各种市场失灵现象。我们看到,公司对成本压缩的狂热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荒谬甚至极具破坏性的境地——由于施工方在构筑混凝土结构时偷工减料,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发生了垮塌事故;石油公司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导致1亿加仑的原油泄入海湾之中。我们看到,大数据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大公司提供了一种新工具,有了这种新工具,它们便可以利用国家安全技术来悄悄追踪并操纵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效率市场的垮塌,甚至见证了整个“市场社会”的崩溃。这样的“市场社会”号称可以通过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但“市场社会”过度鼓励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并因此掏空了我们所有的传统价值和生存意义,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变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文化。消费者经济不断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真正产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深刻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政治立场中立、对极端思想怀有高度警惕的美国公民已经觉醒。
然而,面对冲动的社会这台强大的钢铁机器,我们的各种反叛努力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重建更人性化的价值观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冲动的社会的结构性推动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们的不满所撼动。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以及高速运转的科技创新机器继续粉碎着各种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仍把快速高额的回报当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润和股价哲学仍然控制着管理者的薪酬系统和公司战略的制定过程,美国的政客和政治机器继续靠追求极端主义和快速胜利获取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文化继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只为自己而活和活在当下的理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脱离这种人生哲学的努力都只会增加失败和落后风险。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消费者文化也许是正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对冲动的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与满足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任何远离冲动的社会的可能性都会使我们产生被流放般的痛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也担心脱离冲动的社会意味着极为严厉的经济惩罚,而这样的恐惧显然并不是我们的妄想。现在的社会已不再是我们的祖辈所处的社会:当时的美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实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宽容和激励性的,因为前几代人创造的繁荣允许个人和社会进行适度的冒险。然而,今天美国社会的风气远比那时更加谨慎且充满限制,甚至是充满恐惧。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甚至对冲动的社会的短暂背离(比如拒绝7×24小时待命,或者成为那种“多嘴”的员工)也可能导致我们永远被就业市场所抛弃,这样的风险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即使我们希望在冲动的社会和自我之间创造一些空间,这样的反叛也常常是温和而隐秘的——我们更倾向于悄悄进行某种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动,而不会奢望某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存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中,劳动者不敢离开那份每日杀死他们灵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不愿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行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但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这些可悲的行为中,仿佛每个人都相信,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从短视行为到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的过度消费到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使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文化氛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元素都是社会经济体系进化的必然逻辑结果,顾名思义,这种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应该产出最优的结果。简言之,冲动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论证出,这样的逻辑显然是错误的。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经济后果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我们可以看看西欧的经济模式,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模式,比如德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对经济体系的预期与美国显著不同,那里的人们对过剩现象及不道德现象的容忍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而今天的美国人却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作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只要回头看看美国自己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选择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让我们的经济产出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真正必要的东西。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拒绝承认其他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管这些例子来自国外还是来自美国自身的历史,他们常常将这些情况归纳为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或定性为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入侵——当然,他们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即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结论——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采取行动,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可持续、更平等、更人性化——仍然成立,而且这一结论未必就是一种“自由派”的主张。
早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称呼方式)必须不断接受敲打和管理,才能保证它的高效率让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受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 [1] 今天,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搬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论证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场才是最优的经济形式。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密本人早已认识到,市场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在亚当·斯密所认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中,他尤其支持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并对金融板块实施比较严厉的管制手段,以防止经济权力被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人士所垄断。亚当·斯密认为,这些管理性的干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银行家和其他拥有经济权力的人的天赋自由权”,但如果一个国家确实希望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那么这种对少部分人自由的限制是一项我们必须采取的手段。 [2] 正像荷兰经济评论家托马斯·韦尔斯所指出的:“对亚当·斯密来说,商业社会是一项道德工程,要想取得最大的潜在收益,我们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韦尔斯写道:这项道德工程的成功“绝不是事先注定的,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3] 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一工程的成功与否?在冲动的社会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希望取得怎样的“产出”?为此我们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呢?
非常幸运的是,亚当·斯密关于“整个社会的安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冲动的社会中,由于效率市场的价值观已被充分内化和制度化,美国的文化仿佛一团由无数相互分离的个体组成的电子云。这些个体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美国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国的政党。这些相互分离的个体都在追求自身的个体利益。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形式对个人(至少对某些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因为这种文化鼓励并促成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更多的个人财富、更多的个人消费、更多的个人满足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然而,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却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因为这种文化重塑了个人存在的意义。曾经,每个人都是以“整个社会”一员的身份而存在的,如今,个人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变成了竞争,为了获得个人的满足,我们需要随时与社会其他成员为敌。如今,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赢家通吃的竞争环境中,社会目标,甚至共同财富的概念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因为这种共同财富已不再是一种全社会成员可以分享的财富了。
因此,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种极度不可持续的状态,最能精确体现这种不可持续性的现象便是我们把经济增长率当作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的经济能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工厂、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回报,我们便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样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因为从历史上看,更大的蛋糕确实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分到更多。尤其是在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迅速、高效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还带来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带来了更多新颖、实用的产品,以及更高的社会理想,这提升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然而,自冲动的社会诞生以来,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系逐渐断裂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虽然美国的GDP在高速增长,整个社会却在不断沉沦。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一小部分精英阶层通过高效的金融板块和裙带资本主义所垄断,还因为我们的市场已经重塑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价值观。于是,经济的成功不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成功。事实上,由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具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特点,社会的失败常常是GDP高速增长的源泉。在我们的商业环境中,公司文化日益偏向对快速回报、季度利润以及股价的追求,因此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成功(以及GDP的飞速增长)可能意味着一些严重伤害员工和整个社会的商业策略。正因如此,虽然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雇主对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资不断下降,公司在长期基础研发方面的支出也自由落体般地飞速下跌,美国的公司却可以每年花费5 000亿美元的巨资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并以此获取巨额利润。在冲动的社会的经济模式下,真正有意义的生产活动和仅仅能为资本提供高效回报的活动没什么区别,因此,虽然每年劳动者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上逐年下滑,股东却继续享受着人为创造的虚假利润,然而没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
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沉沦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商业世界。事实上,在冲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冲动的社会中,一位重病患者比一个健康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能为医疗系统创造更多的利润。小镇凋敝的商业区比繁荣、富有活力的商业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意味着全球化的零售供应链又成功消除了一处低效的商业区。森林的过度砍伐、过度的信用卡消费、不断上升的碳排放量、处方药滥用现象的盛行,这些都被算作经济净增长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成本的系统中,这些活动都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同样不合理的是,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正确计算各种活动的社会成本,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很多在正常经济渠道之外创造出来的真正财富。只要不涉及商业交易的活动,一概不被计入GDP的增长,这些活动包括在老年中心的志愿者活动,在家教孩子们烹饪而不是外出就餐的家庭活动,晚餐后陪孩子们玩耍而不是让他们一直抱着电子设备——虽然这些活动对经济的健康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活动不是可以被购买的商品,它们便不能被计入GDP的增长。记者兼政策专家乔纳森·罗曾这样讽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美国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运行的家庭,他们自己烹饪餐食,在晚餐后外出散步,他们进行真正的交谈,而不是在商业文化中放养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与孩子交谈、用散步取代开车,这些活动都不需要花钱,因此这些家庭会比其他更为商业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关系意味着在婚姻咨询及离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GDP标准,这些良好的家庭关系都威胁着经济的健康。”
几十年来,各领域的积极分子不断呼吁放弃目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指标的评价标准,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度量指标,这种指标应该能够反映被效率市场所忽视的各项成本与收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建议以一套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取代GDP指标,这种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将各种非金融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列入考虑。这些经济学家希望,这种新的度量系统能够逐渐鼓励国家和公司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经济成功的定义。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在事后曾这样解释道:“你的衡量标准会影响你的行为。如果你的衡量标准不对,你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 [4] 然而,这些学术上的早期努力并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当某联邦机构试图研究一套新的GDP衡量标准时,国会甚至以取消给该机构的资金支持相威胁。然而,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关于新的经济度量标准的观点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们的经济究竟应该以什么类型的产出为目标?这种新的、生产力更高的经济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展开了非常广泛和必要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尚未完全切中问题的关键,但是,在这场我们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斗争中,这一讨论的展开无疑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场讨论中,已经涌现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提议,而这些提议显然不是为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准备的。另一位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目前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教父级人物。戴利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稳态经济模式” [5] ,在稳态经济模式下,整个社会积极而细致地使用管理、税收和其他政策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目标是将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可再生、可降解的范围之内”。 [6] 将经济增长控制在自然极限的范围之内,这一概念在环保主义者的努力下继续发展。在这批环保主义者中,比尔·麦吉本提出了深度经济的概念,在这种深度经济模式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将目前GDP度量指标没有考虑的三种产出最大化:一是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二是收入的平等,三是人类的幸福。几年前,麦吉本在接受《沙龙》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这样的经济更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样的经济将人类的满足看得与物质富足一样重要。这样的经济除了重视规模的增长,也非常重视经济的持久性。” [7]
还有很多类似提议,这些提议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或多或少地要求我们必须彻底重组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因此,这样的提议很难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拒绝这类提议,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未真正尝试,甚至从未考虑过市场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模式。我们目前的文化虽对经济模式的现状越来越悲观,却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改善。我们更愿意接受那些贴着自由派和渐进式标签的改革提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规模较小、政治上较为可行的修补性措施来修正经济体系的前提假设和目标,从而把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推向一种更可持续的、更人性化的轨道。比如,很多关心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家(以及比较有经济头脑的环保主义者)都希望在现有的GDP指标中加入一个度量碳排放量的指标——这一指标度量的是美国经济每产生一美元的经济产出会造成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人希望,在引入这一碳排放度量标准后,可以对碳排放进行征税。从理论上说,通过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市场就会自动寻找碳排放量低甚至无碳排放的新技术。当然,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对碳排放税的构想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很多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包括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如里根政府的顾问阿瑟·拉弗和罗姆尼的顾问格里高利·曼昆)都表示,他们认为碳排放税最终会成为控制碳排放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且他们相信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下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8]
除了碳排放税,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渐进式的改革方针,例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考虑这些经济增长为人类带来的福祉,并引入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度量这种福利效应。比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及其同事阿马蒂亚·森提议,我们应将那些直接影响人们真实生活水平的指标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这些指标不仅包括个人收入,还包括人们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以及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 [9] 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对目前的政府度量标准(比如美联储的通胀目标)进行调整,使得这些目标能与新的、更具社会进步意义的目标相适应。比如,迪安·贝克和保罗·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央行过度强调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并因此对政府开支进行了很多不必要的紧缩性削减,这正是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迪安·贝克说:“自然失业率并没有上升,目前失业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有问题。”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影响很多经济产出(比如失业率,比如人们能获得怎样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像很多自由市场支持者及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对这些情况无能为力。政府手中握有各种杠杆(比如税收、补贴、管理措施等),通过调节这些杠杆,完全可以改变经济的社会“产出”,使其更符合民众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偏好。然而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使用了这些杠杆,错误地让市场决定社会产出的最优组合以及各种互相竞争的社会目标的最优平衡点。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哲学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我们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和选择,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也会越来越倾向短期的、不公平的、不可持续的产出模式。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不同的结果,就必须将经济从自动驾驶的模式中解救出来,重新掌握经济活动的方向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该走向何方,以及经济的重点和价值何在。在目前的经济模式下,经济产出的成果日益偏向资本一方,我们对这样的现状满意吗?我们是否觉得应该重新向劳动者一方倾斜?我们是希望技术创新的永动机致力于渐进式创新以及高速的回报,还是想投资于风险更高的技术研究,以催生新的产业,并解决一些严重的资源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容忍现存的经济模式,继续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保护那些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还是使劳动者享有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同样的机会、安全感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这些问题显然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要想给出合理的答案,我们必须做出实质性的取舍。要处理好这些取舍,我们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还需要有思考和妥协的意愿。但美国目前的政治文化(甚至整个冲动的社会)不仅不能对这些行为予以奖励,还将它们视为低效率的元素,想方设法回避甚至淘汰这些元素。
但不管怎么说,设计出一套新的度量标准可能成为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控制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可以不仅仅着眼于GDP,不仅仅计算公司的净利润或净亏损,转而更全面地评价整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这套新的度量标准将迫使我们展开一场更广泛、更社会化的讨论,探讨我们将采取怎样的价值观,以及为了支持这套价值观我们必须做出何种取舍。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套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能采取追求这些价值的实际行动。而这样的实际行动是极为关键的。可能会有人认为,因为这样的行动最终必然要依赖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民主过程中的各种妥协让步,因此我们应该在政治领域中迈出第一步。然而,由于冲动的社会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方面的,更具体地说是公司方面的,因此我认为从逻辑上说,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步甚至最初几步应该在商业领域进行。(事实上,这一点目前已经在讨论了。)面对整个社会的总体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商业领域入手,改变商业机器的前进方向。
几十年来,保守派人士一直对美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抱有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施加了过强的影响,而正是这样的干预行为导致美国的经济无法继续之前的繁荣。如今,我们可以对美国金融市场做出类似的指控。现在,金融市场已经穿透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弊病。从消费者信贷的过度扩张到“激进”股东群体的兴起,金融板块逐渐将其对高收益、快速回报以及资本效率的需求注入了消费者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时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金融化过程最臭名昭著的症状便是对消费者信贷的过度使用。显然,要想对冲动的社会发起实质性的攻击,我们应该帮助消费者重新思考他们为了追求即时满足而透支消费的行为模式。然而,更重要的是,金融化严重影响了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的行为,而美国的大型公司在提供就业机会、科技创新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想打破冲动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创造或重现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更能产生社会效用的经济体系,最关键的步骤之一便是减少金融市场对商业界的影响。
在公司层面,金融化过程最有害的副作用是对公司短视战略的鼓励。在这样的短视战略下,公司常常牺牲长远的可持续性,只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界曾愿意在科技创新以及劳动者培训方面进行大量的长期投资,而现在为了取悦同样短视的大投资者,公司在上述两方面的投资数额都大幅度缩小了。为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必须废除当前鼓励投资者和公司采取短视策略的激励机制。而关于如何废除这样的激励机制,目前已经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提议。很多专家建议引入金融交易税制度——投资者每次买卖手中的证券、衍生品和其他金融资产,都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款。这样的金融交易税政策能够增加靠追逐短期股价变化牟利的成本,从而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而一旦投资者的投资期限拉长,公司追求季度利润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小,于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便能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制定成本压缩、员工培训以及创新投资等方面的策略。
另一些提议则试图通过改革目前极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模式来改善扭曲的激励机制。比如,有些人提议,可以用限制性股票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一部分。这种限制性的股票在高管离开公司后的5年或7年内禁止出售,于是在这样的薪酬机制下,高级管理人员便不能通过快速提高公司利润来谋取个人利益了。 [10] (其中的一项提议更是提出,公司甚至可以追回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薪酬。《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样的薪酬机制可以让“建立在短期投机基础上的公司立刻爆炸”。 [11] )另一项有趣的提议则建议,可以把公司高管的薪酬与科技创新联系起来:高管的薪酬高低取决于公司目前的利润有多大比例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带来的。 [12]
公司的高管们显然不会对这些提议展示出多么热情的态度。然而,研究公司薪酬和公司管理策略的专家们指出,很多公司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这方面的提议,并借此机会把高管的薪酬重新纳入可控的轨道。天文数字般的高管薪酬不仅伤害了员工的士气,还招致媒体和政界的不断批评,更严重的是,目前的数据显示,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公司的业绩表现之间通常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13] 事实上,有一项研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项研究发现,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中,每五位高管中就有两位来自业绩极差的公司:这些公司要么不得不要求政府救助,要么传出欺诈丑闻,要么干脆以破产告终。
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支持对商业板块进行去金融化处理的专家还呼吁对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因为目前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向高管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害的巨大诱惑,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金融工程人为抬升公司股价,从而大幅提高自己的薪酬。反对公司股票回购策略的人指出,只要撤回里根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82年做出的一项规则改变,联邦政府就可以十分轻松地全面禁止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在这条规则改变出台之前,回购本公司股票曾被正式界定为非法操纵市场的行为。而事实上,股票回购策略确实是一种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因此禁止这样的行为是十分合理并具有充分法理依据的。
所有上述动议的共同点是试图将公司推离短视的轨道,让它们重拾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样的变化可以带来很多领域的深刻变革,如在科研方面的长期投资将大幅提升。而对未来的劳动者而言,这项改革将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推行这样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阻挠机械自动化的趋势,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对国际贸易采取抑制性政策。在这些改革措施之下,公司可以显著改变上述趋势对劳动者的影响,因为这些改革的目标是重塑公司对劳动者的重视。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够成功实施,公司将不再把劳动者视作削减成本的渠道,而会把他们当作需要认真保护并不断升级的珍贵人力资源。在股东革命的过程中,上述价值观几乎已被完全抛弃——管理者们不遗余力地追求降低成本以提高公司的季度利润和股价,他们大幅削减员工培训方面的投资,一旦劳动者无法在与机器或廉价外国劳动力的竞争中胜出,便立刻无情地将他们解雇。在公司大批裁员的同时,政府和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可行的努力,这又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危机的升级。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要求公司在协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强制再培训能够保证员工的就业技能(即人力资本)不致在裁员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欧洲的公司能以较快的速度使失业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而在美国,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工作向来不够全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盛行保守派反税收、反政府的政治主张。因此,美国针对长期失业问题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十分短视的政策。虽然美国扩大了失业补助的适用范围,并对这项政治成就沾沾自喜,事实上我们从未认真处理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在失业工人试图对自己进行再培训并重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说:“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在美国,这造成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浪费。有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本正是我们(实现制造业复兴)需要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声称我们需要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被无情地扔出了劳动力市场,根本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机制来维护这些人力资本。”
对今天的很多自由派人士来说,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提高对公司的征税,对持续增长的公司利润进行再分配,然后用这些资金发展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领域,比如员工的再培训。自由派的这种意见有很强的说服力:自2000年以来,保守派不断推进的减税政策已经导致税收收入无法支持美国政府庞大的开支(包括两场战争的开支以及经济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支出等)。为了防止保守派人士的选择性遗忘,在此我必须指出,这已经不是保守派人士第一次将减税政策推行到过分的地步了:1981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推出了大幅减税政策。此举导致美国的国家债务水平翻了四番还多,达到了30 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14] 然而与目前的情况不同的是,里根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并在接下来的7年中4次推出了增加税收的政策 [15] ,其中包括史上最大幅度的公司所得税提高,还包括大幅提高薪酬税用以支持联邦医疗保险系统的支出。 [16] 然而,今天的保守派已经变得如此偏执,反税收和反政府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于是,即便美国劳动者在福利和保障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即便美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已变得日益破旧不堪,增加税收仍是一个禁忌话题。
然而,在给自由派人士戴上提高税收和增加开支的帽子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提高公司的税收,然后再用这笔资金对被公司抛弃的员工进行再培训,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相当荒谬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方法,即通过政策手段(比如税费减免)鼓励这些深受谴责的公司把税前利润的一部分用于保护和升级其劳动力“资产”。比如,拉佐尼克认为,美国的大公司只要从它们目前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资金中挪出一小部分用于在职员工培训,就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这样的政策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裁员。即便被裁员,失业的劳动者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以苹果公司为例,目前苹果公司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资金高达1 000亿美元,只要从这1 000亿美元中拿出5% ,苹果公司就可以为员工设立一所公司内部的学校。这所学校的雄厚资金能保证他们可以请来一流的授课人员,向员工提供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这些技能不仅在苹果公司内部有用,而且在整个技术领域同样能发挥作用。拉佐尼克认为,苹果公司应该向所有员工免费提供这样的培训项目,这其中当然包括目前在苹果公司零售店工作的近40 000名销售人员。这样的培训项目不仅可以帮助苹果公司的员工获得公司内部的晋升机会,还可以让他们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拥有更多的工作技能和更有分量的简历。拉佐尼克指出,这种公司内部学校的培训形式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公司能够认识到扩大高技术的从业人员数量是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然而在美国,很多公司却采取了典型的冲动的社会式的短视策略:当面临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时,公司往往选择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即游说华盛顿当局调整移民政策,从印度等国引入更多拥有这些技术的移民。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仅靠少数富裕公司为员工建立内部学校并不能让美国公司重新扮演战后时期那种家长式福利机构的角色。但是,这样的改革可以向美国的整个商业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毕竟学习和模仿像苹果这类超级成功公司的经营战略向来是美国商业界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可以清晰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目前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不可持续的。也许,在30年以前,降低劳动者地位、把劳动力仅仅视作公司的一项“成本”的行为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公司策略已经造成了劳动者对雇主的不满和仇恨,从而增加了公司自身的管理难度。适当放弃这种不可持续的策略,公司可以在员工和效率市场对利润的冷酷追求之间创造适当的距离,这样的改革措施也许能够帮助美国的公司重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曾让美国的劳动者骄傲地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生产效率,然而效率市场的冷酷机器却把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作一种低效率元素而无情地粉碎和消除了。
然而,在冲动的社会走向终结之时,我们不可能依靠公司自发的努力(如对员工的再培训以及对短视策略的反省)来修正经济不平衡现象。 [17] 在我们的经济中,金融化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只有外界的干预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平衡。否则,在目前追求快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下,我们迟早会迎来灾难性的修正过程。显然,如果我们真的决心实施这种自上而下的、德拉古 [18] 式的干预手段,那么最需要干预的显然是美国的金融板块。目前,金融板块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修正自身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相反,华尔街那些大型投行不仅仍在进行各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而且这些高风险行为的性质和2008年拖垮整个美国经济的投机行为毫无二致。同时,由于这些华尔街的投行规模巨大,事实上防止金融危机的常规监管手段都不能对它们起到真正意义上的限制作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美国银行业69%的资产都掌握在摩根大通、花旗集团、高盛等12家银行手中。 [19] 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所占的份额如此巨大,因此无论它们做出怎样不负责任的恶劣行为,美国政府都不可能任由这些机构倒闭,否则美国的整个经济就可能成为它们的陪葬品。事实上,这些超级银行不仅因为规模巨大而不可能倒闭,而且政府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它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犯罪活动,而政府居然不敢对它们采取法律诉讼行动。2013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侯德曾公开承认,由于这些美国超级银行的规模过于巨大,“如果我们对它们提起刑事诉讼,就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状况”。 [20] 这足以证明,华尔街的这些超级银行不仅“大而不倒”,甚至已经到了“大而无罪”的地步。
正因如此,很多金融政策专家早就指出:如果不把这些“大而不倒”的超级银行拆分成一些规模较小、更容易管理的金融机构,我们就不可能对金融化经济的风险真正予以限制。然而在目前两党对立的政治气候之下,这种极端化的政策手段被普遍认为是无法真正实施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拆分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只有这种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才可能在目前瘫痪的冲动政治体系中为未来的突破扫清道路。
现在,冲动的社会的最大盟友不是永不停歇的技术跑步机,也不是市场对效率的狂热追求,而是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关于政府角色争论的僵局。在处理社会弊病方面,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方面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发生过明显的变化。美国的主流民众曾经持有一种自由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且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此后,这一观点被一种同样荒谬的保守派观点所取代,那就是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也根本不应该试图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当然,针对后一种观点,保守派确实可以提出一些支持性的证据。在资源分配、结果预测以及限制个人的野心方面,政府确实从未展现过高超的能力或惊人的效率——因为这属于市场比较擅长的领域。同样,政府也永远无法取代社区、家庭或者个人自给自足的价值观——虽然政府常常进行这种无谓的尝试。但在上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政府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可以为上述经济和政治功能的实现创造足够的空间。政府可以有力地监管寻租者和博弈者的腐败倾向,从而鼓励市场在分配和激励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效。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向美国民众提供针对物质风险的必要保护,使民众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价值,从而组成更富活力的社区和家庭。比如,政府可以保护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事故和自然灾害的伤害,也可以保护少数派免于多数派的专制和迫害。当然,与本书更为相关的是,政府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市场的侵害,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伞,强有力的市场机器将轻易地摧毁美国的家庭、社区、传统以及文化。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市场机器对个人的无情碾压。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干预以来,出现了很多导致社会体系瓦解的经济现象,冲动的社会的崛起也加速了,这种时间上的相关性显然不是出于偶然。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承认政府角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是一种自由派的观点。事实上,这正是早期共和党人的核心政见之一。在进步时代 [21] 中,充满改革动力的共和党人相信,如果任由公司自行发展,公司的高效率、高技术以及垄断策略会使它们不断恶性通胀,而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如果这样的干预确实是必需的,显然现在就是干预的最佳时间点。然而,由于我们的政治文化已被冲动的社会严重腐蚀,这样的干预迟迟无法实施。我们的政治文化受到了金融化力量的污染,金融化的力量把整个政治过程变成了又一个“商业板块”,这一板块和金融板块本身几乎无法区分,而金钱也已经变得和选票一样重要。同样严重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品牌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整个政治过程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瘫痪。这种保守派的品牌文化拒绝承认政府所能发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也拒绝承认正是政府角色的缺失导致金融化力量的腐败现象不断伤害着我们的社区、家庭和个人。美国的保守派人士曾经为保存传统的价值观而努力斗争,然而现时的保守主义品牌文化却一再站在这些价值的对立面,帮助冲动的社会更快地消磨和摧毁这些价值。
然而,在这些矛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前进的道路。在呼吁金融改革的声音中,一些最为激烈的呼声恰恰来自保守派人士。同样,当奥巴马政府拆分华尔街超级银行的努力失败时,当奥巴马政府无力限制这些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行为时,不仅很多自由派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很多右翼人士也同样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对于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言,政府对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隐性担保以及用公共资金救助上述机构的行为显然是一种扭曲市场的政府补助行为。正是这样的政府补助使得这些“大而不倒”的超级银行敢于冒小型银行不敢承担的风险。保守派经济学家、时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主席的理查德·费希尔曾这样说道:“这些公司只收获其行为的正面利润,却拒绝为其错误行为付出代价——倒闭和关停。这已经违反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美国是一个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执行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 [22] 最能体现保守派对“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愤怒情绪的例子之一是,2013年,铁杆保守派人士、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维特决定与来自俄亥俄州的极端自由派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携手推动一项要求超级银行大幅降低负载程度的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在华尔街的强力游说之下未能通过,但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保守派评论员佩奇·努南,以及《华盛顿邮报》的乔治·威尔。(乔治·威尔认为,华尔街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机构充分证明,“将损失社会化,同时却保持利润的私有化,这样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23] )换句话说,在试图重新对“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实施管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曾经有机会驯服金融化的有害力量,还曾经有机会开创一种我们急需的左派和右派互相和解、互相合作的政治空间。在赢家通吃的品牌战争开始之前,这样的两党合作机制曾经是政治体系的常规模式。
这种两党和解的时刻将以怎样的形式发生?我们不妨充分展开想象。也许一切的开端是美联储的费希尔登上福克斯新闻频道,向公众介绍他与同事在2013年年初制订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大而不倒”的华尔街银行强制拆分为规模较小、容易管理的金融机构。(该方案的关键是,撤销联邦政府对除传统贷款行为以外的所有金融行为的安全网络保障,并赋予管理者权力,使管理机构能够强制拆分那些不愿自主重组的金融机构。 [24] )费希尔的这一方案不仅会激起保守派舆论的强烈反响,同时也会获得左派媒体的广泛宣传。随着民意支持的不断膨胀,参议员维特和布朗将把费希尔的计划拓展成为正式的立法法案,而这一法案将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当然,华尔街那十几家“大而不倒”的银行机构必然会花重金进行游说,试图阻止法案通过,但由于这一运动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华尔街的游说力量不会获得太强的谈判筹码。即使这些超级银行能够避免被全面拆分的命运,它们也很可能会被迫接受某种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类似的法律规范。(出台于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曾在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业务和投资行为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金融板块中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被一举消除。同样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内外,两党显示了在全国性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携手合作的能力。这种政治上的成功将给冲动的政治体系致命一击,因为冲动政治体系的养料正是两党不和及政治机器的失灵。这样的政治成功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政治过程完全有能力做出实质性的行动和改变,于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分别建立起来的分化的政治品牌都会因此受到削弱。
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佐治亚大学政治科学家基思·普尔是研究政治两极化的专家。普尔指出,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曾出现过去两极化,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对美国的商业界实施改革,两党的中立派人士在这一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团结一致,进行了共同的努力。普尔认为,要想让这样的历史重演,我们需要在选举中看到两党都出现一些中立的候选人。虽然在深度两极化的时代这样的情况无法出现(因为两极化的程度越高,中立候选人胜出的概率越小),然而这样的现状是完全有可能改变的。普尔指出:“如果在国会中两党之间有更多的政策需要共同推进,那么,对候选人来说,采取中立的立场就会显得更有吸引力。” [25] 而拆分华尔街大型银行的运动很可能促成这样的情况。
即使是品牌政治的暂时弱化也能为与冲动政治的斗争提供极为重要的滩头阵地。一旦中立人士加入了对冲动政治的战争,国会就可能有能力向竞选金融问题开炮。竞选金融是最深层次、最高级的金融化现象,也是冲动的社会的终极表达方式。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生效以来,来自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亿美元助选资金导致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金融化。我们的政治体系不再只是以市场镜像的形式出现,而是完全融入了市场之中。从传统上说,这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比较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如伊丽莎白·沃伦以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也确实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根据《资本纽约》杂志的报道,科莫曾表示:“这是一个能带来全国性影响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至少与同性恋婚姻和枪支管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26] 然而,竞选金融问题同样也可以成为让保守派人士团结起来的议题。事实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原则一直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则之一。至少在疯狂涌入的助选资金成功腐化左派力量和右派力量之前,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原则曾经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则之一。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父巴里·戈德华特曾在1960年这样说过:“为了让政治权力获得尽量广泛的分布,对政治选举活动的金融资助只可以来自个人。我认为工会或公司都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理由。因为工会和公司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创立的,因此它们所参与的活动也应该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虽然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对推进竞选金融改革毫无兴趣,然而却有迹象表明,竞选金融问题让华盛顿以外的保守派人士着了火。民意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和州立法决策者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公司、工会及其他组织排除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外,同时禁止上述组织对竞选活动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其中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每10位共和党人中有7位支持通过上述宪法修正案。 [27] 红州网站的一位保守派博主克里斯·迈尔斯这样写道:“事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们认为政府为了保护大公司和大型工会的利益而践踏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但是,保守派完全有机会向公众清楚地表明,我们代表和捍卫的是人民真正在意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达到的目标吗?” [28]
有趣的是,随着茶党的垮台,我们看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领袖已经逐渐远离冲动政治的保守主义品牌,开始向中立的立场移动。一位《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指出:中间偏右的智囊团以及实用主义的保守派政客中已经涌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改革派保守主义”,因为这批人认为,目前保守派人士的错误前进方向无异于在一条自杀的道路上狂奔。改革派保守主义的主张包括:改进早期幼儿教育系统,还包括让各州分别征收燃料税,并靠这笔资金自主管理本州的交通项目等。这些主张展现的是传统保守主义注重实际问题的现实精神,而这种理念对中立的美国公众来说一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同样重要的是,现实精神曾经是美国两党妥协以及有效立法过程的基础。在税务改革等重要政治问题上,法案的通过总是靠左派和右派中的实用主义者找到两党合作的途径。在冲动的社会的品牌政治文化中,实用主义成了最先被牺牲掉的元素,然而,历史先例使我们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让实用主义精神重新回归我们的政治体系。《纽约时报》的另一位保守派评论员戴维·布鲁克斯指出:19世纪的保守派政治家,如亚伯拉罕·林肯、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其他辉格党人,通过关注一些基本的、与党派无关的议题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强烈支持。这些议题包括社会流动性、经济机会以及“如何用政府权力保证美国非主流群体中的个体能拥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的工具”。这个早期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中立政治的威力。布鲁克斯还写道:更重要的是,辉格党人主张用这种实用主义的中立立场取代“持分离民粹主义立场的杰克逊追随者们”推行的充满敌意的两党斗争策略。因为对实用主义的辉格党人而言,“与其挑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如帮助民众向更高的阶级迈进”。 [29] 布鲁克斯认为:今天这样的“机会联盟”也能够赢得同样广泛的公众支持,并彻底“打乱现存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机会联盟应该关注提高社会流动性的途径,比如重建早期儿童教育系统或者帮助条件较差的家庭创造更好的儿童教育模式。虽然自由派人士可能会全盘否定这样的运动,并认为这是共和党人在内斗的崩溃边缘为自保而进行的垂死挣扎,然而改革派的保守主义仍然可能是我们达到一种新的中立政治的第一步,因为改革派的保守主义主张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管左派还是右派的品牌政治都从未真正回应过我们的诉求和理想。这种现实主义运动很可能标志着团结各派的实用主义政治的开端,在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中,我们将把目光重新集中在关于共同利益的讨论上,并以寻求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为重点。不管这样的实用主义运动多么不成熟,它仍然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们已经正式开始抛弃互相攻击的品牌政治,重新走向关注现实、关注可能性的政治文化。
假设这种关注可能性的政治再次成为可能,显然要想把冲动的社会重新推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对金融业重新实施管制。将金融元素排除出我们的政治体系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此举可以让我们用政治去引导投资领域的决策,让美国重新承担起主要公共投资的长期义务。简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比如做出最有利于社区和公众利益的长期承诺,因为个人、社区或者公司都缺乏完成这种任务的能力和意愿。一个世纪前,美国的进步改革运动正是以这样的理念为核心逻辑:随着成熟的消费者市场完全掌控个人商品方面的投资决策,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干预来保证公共商品领域也能获得足够的投资。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左翼和右翼力量妥协的空间。当然,自由派人士必须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实质性的福利改革(比如对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测试和修正)以及管理改革(尤其是对小型公司的管理改革)。同时,保守派也必须放弃他们顽固的品牌意识,并且承认几十年来不断减税和两党的预算战争已经导致目前美国面临公共投资方面的严重不足。事实上,美国在公共投资方面的赤字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经济体。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相关例子:在公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建设方面,美国每年的实际投资大约比所需投资少2 500亿美元。 [30]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的各个地方,很多州政府正放任数千英里的道路因为缺乏维护修缮而逐渐“化为沙石”。 [31] )在37个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每位儿童身上的早期护理及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名列第28位。世界上有23个国家拥有比美国更快速的宽带网络。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一长串这种让我们感到尴尬的例子。比如,目前美国仍有90%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而目前中国政府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的投资几乎达到了美国的两倍。
要想扭转这些公共投资方面的赤字,我们必须对目前的政治文化做出显著的改变。目前,美国的政治文化被品牌化的保守主义所控制,而这种品牌化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反对一切增加赤字的政府支出,甚至反对适度增税。然而,如果能够获得两党的支持,政治领袖们就可以开始提出和推行在某些方面增加投资的动议(比如在基础建设和能源方面)。这样的政治运动将重点强调公共投资对促成美国过去经济繁荣时期的重要作用。(不仅包括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还包括互联网繁荣时期,因为如果没有之前几十年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根本不可能出现这一轮网络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应该倡导今天的我们做出与过去类似的承诺(比如,用大量资金支持下一代能源技术研究工作),这样的承诺能够点燃美国经济加速的引擎。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美国能够大量投资核聚变领域的研究,就可能产生出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新技术,从而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核聚变能源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因为核聚变的过程只产生少量放射线,而且核聚变能源所需的燃料(氢的同位素氘)从海水中就可以大量获得,这种燃料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通过发展核聚变技术,我们有希望获得一种全新的能源,这种能源不仅碳排放量低,而且比目前市场上的任何能源都便宜许多。由于目前能源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新技术完全可以深刻地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并创造出一系列新的产业,或者将现存产业大幅扩大。所有这一切都能使我们逐渐减少对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能源的依赖。目前,美国政府对核聚变研究的资金支持正在不断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美国政府对核聚变技术进行中等程度的支持(根据一些研究的估计,要在2034年之前发展出一个可以产生能源的核聚变反应堆,大约需要投入300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产生惊人的社会回报。显然,没有任何私营公司愿意进行如此巨额的投资,也没有任何私营公司愿意花那么长时间等待回报的产生。因此,这种类型的投资正是政府应该也有能力进行的公共投资。用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的话说:核聚变能源“是公共产品的一个极好的例子,私营板块没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公共产品,而公共板块则应该对这样的公共产品给予足够的重视”。
必须承认,要推动公共投资的提高意味着政客们必须做出一些直言不讳的长期政治承诺,而如今主流的政客越来越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在一个高度金融化的、以民意调查结果判断政治成功与否的冲动的政治世界中,与其试图领导民众,不如用各种高效的手段去迎合和操纵民众。同时,由于长期的文化引导,选民已经产生了对公共投资,甚至对整体政府行为的恐惧,因为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被宣传为低效率的、不正当的,甚至是腐败的。但对那些真正有决心抛弃品牌政治的政治领袖而言,美国历史上能赋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的成功例子并不少见。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承诺要在1970年之前将美国人送上月球,并因此成功赢得了选民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建设计划也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虽然这一公共交通工程是当时整个人类历史上造价最高的工程。在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成功引导选民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而在此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则为加大教育、公园及公共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当然,要说服选民接受上述项目并不简单,这需要极高的宣传技巧。比如,为了说服选民支持增加在公共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富兰克林·罗斯福巧妙地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经济理念,这套经济理论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国家经济陷入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的方式拉动需求,从而达到重振国家经济的效果。
然而,我们今天的政治领袖却不再具备这种说服选民的能力。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这不仅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未能推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改革,还因为奥巴马政府既不愿意攻击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也未能有效地向选民宣传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从而对原有的经济政策做根本性改变的必要性。有些经济学家和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宣传方面的能力和意愿有限,而一些更尖锐的批评则认为,是奥巴马政府与华尔街的紧密关系导致了这届政府在这方面故意不作为。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美国公众在情感上深切地呼唤一场“我们能够信赖的变革”,但大多数美国公众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迎接这种我们需要的根本性改革。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由于对自己的经济情况高度焦虑,对政府和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我们已经失去了超越个人利益、为更宏大的目标而努力的信心和决心。换句话说,即便这届政府想要推行这样的变革,公众也无法向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正如《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奥巴马“早已认识到,如果无法获得外界组织的支持,一位总统能做到的事情实在是非常有限的”。 [32]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改变群众不愿参与政治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来扭转公众对政治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对政治体系进行清理,从而让国民重新产生参与政治的意愿。我们可以通过推行经济改革和提高公共投资,重新创造出上几代人所拥有的经济机会,而这样的经济机会能够启发和引导人们走出自身利益的狭小天地,去追求某些更为宏大的理想和目标。通过重塑公众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及市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平衡,我们可以让公众的政治眼光变得更加无私、更加开放和更加长远。
诚然,如果公众不希望这样的变化发生,那么上述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变革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几十年来的情况,让公众相信这些理想主义的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腐败让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冷酷和愤世嫉俗。消费者市场不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们不需要政府和政治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获得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主流文化逐渐接受了市场控制社会的现状,虽然这样的社会体系正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平等现象。但是,在个人层面,上述默许态度正在逐渐改变——因为对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维持现状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面对中产阶级的衰落、商业界的短视行为以及迫在眉睫的基础设施故障问题,人们已经无法保持沉默。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今天普通的美国人却时刻担心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我们已经无法再忽视和回避这种荒唐的现象了。也许我们曾经相信,我们的市场和政治体系会通过某种方式自动完成对自身的改革,然而,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再相信这样的说法了,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的系统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已经不再有否认和回避的资本了。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些让冲动的社会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元素(政治体系的顽固失灵、长期以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个人的慢性自我中心症)本身就是冲动的社会的一部分,这种巨大的垄断品牌效应使得实质性的改革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这种品牌效应,并且明白改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现在,一些精英统治论者、学者、有改革眼光的政治家以及商业界人士已经打响了对短视的政治体系和商业系统的战争,而我们中的其他人应该把思想化为行动,投身到这场对冲动的社会的战争中去。不安和紧迫感已经笼罩了整个美国社会,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向我们自己,同时也向更广阔的社区展示出我们的信念:变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驱动冲动的社会的那些制度因素完全可以被我们所改造,成为抗击冲动的社会的掩体。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把她内心的这种不安的情绪转化成了实际行动。玛西当时是一家全国性建筑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她却开始严肃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玛西喜欢设计各种建筑,然而如今的建筑行业却被削减成本、增加数量的想法所把持,创造性在这一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玛西告诉我说:“大部分时候,我的工作任务只是研究怎样从工程中赚钱。有时我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每个人都喜欢我的方案,然而接下来他们会说:‘好吧,让我们来谈谈划算与否吧,让我们拼命压低成本吧。’于是我开始想:‘我设计的这栋建筑会在那里存在50年,我的名字会出现在这座建筑上,我并不认同我们现在的这些做法。’”玛西当时恰好会参加一些本地学区的志愿者活动,她带领学生们参观和欣赏市中心的建筑,并进行讲解。玛西非常喜爱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好奇心,在每次志愿者活动的几个小时中,她都相信她的努力可以改变孩子们看待世界的视角。玛西渐渐觉得,这些小小的转变比她在工作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创造力,也更加重要。
有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玛西在车中收听了一档广播节目对一位政客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政客谈到他是如何辞去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而投身政治的。那位政客引用了大希列尔的一句古话:“若仅为己,我为何物?若非此时,更待何时?”听到这句话时,玛西受到了触动。“当时我想,这句话不正说出了我的感受吗?我想去做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于是,玛西辞去了工作。她离开了之前供职的建筑公司,重返校园去学习教育硕士的课程。现在,玛西每天的工作是“设计”高效的课堂教学内容。她告诉我说:“我现在终于拥有了我想拥有的影响力。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和一个孩子进行一场对话,而这场对话有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玛西承认,辞去建筑公司的工作并不容易。放弃这样的工作不仅意味着放弃高收入,还意味着她再不能获得这种所谓的光鲜工作带给她的自我满足。玛西说:“当我告诉别人我是教师的时候,对方常常赶紧换话题。”然而,当玛西离光鲜的商业工作越来越远后,她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市场定义的职业成功与她的个人价值观所定义的成功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对玛西来说,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参与并影响他人的生活。玛西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成长和领悟,我对自己说:‘也许教小朋友真的比想象我自己在设计房屋更重要。’是的,那是真的。我热爱现在的职业,而且我从来不往回看,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对我来说,玛西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制造空间”的主题。只有当我们退出冲动的社会的价值和规律时,我们才能看到冲动的社会存在多么严重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自己如何建设性地回应这样的失衡现象。我们曾讨论过如何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制造空间,以及如何在市场和政治之间制造空间。但是,要想真正摆脱冲动的社会的束缚,我们必须让自我和市场之间的缝隙变得更宽,必须扭转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和市场的融合过程。只有这样,自我才能获得一些呼吸的空间,才能稍微远离市场短视的价值观的污染,重新获得那些更重要、更长远、更人性化的价值观。同样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后退一步时,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在消费者市场中狂热追求的那些东西事实上只有在其他地方才能获得。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如今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是“连接”,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半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曾说,人们一直“被对社区的渴望驱动着”。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仍然被这种渴望所驱动。显然,从定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即时满足的消费者文化中满足上述需求。事实上,我们所追求的这种深层次的连接恰恰是一种与冲动的社会的精神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所渴望的,是与某种永久性的、比自我更宏大的东西的联系。当我们在市场中寻找这样的连接时,我们不仅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且破坏和削弱了可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选择了后退。事实上,这场后退运动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在美国各处,人们采取了上亿种反抗冲动的社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反映出我们不同的偏好、恐惧和选择。尽管这些反抗行为多种多样,但我们最终必须认同某种更宏大的统一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些对连接和社区的个人追求转化为某种更广泛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因为只有这些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才能保护和重塑社区的价值观以及某种更宏大的长期目标。显然,只有集体行动才能让上述一切成为现实。如果说,在冲动的社会的腐蚀下,自我和社区的概念同时出现了垮塌,那么在反抗冲动的社会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同时重建自我和社区的功能。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已经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理解,冲动的社会诞生的关键以及制服它的关键都在于自我和社区的关系。当自我和社区之间存在健康的关系时,自我和社区之间可以赋予彼此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社区是健康的社区,而社区的基本价值(共同的目标、合作、自我牺牲、耐心以及长期承诺)也能对自我起到支撑作用,并赋予自我回馈社区的能力。这样的关系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自我和社区可以互相支持并提升对方的作用。是的,我们曾经使这样的良性关系瓦解了。我们曾错误地说服自己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对市场的依赖获得所有需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再需要社区的帮助,只要让社区自生自灭就可以了。然而,随着追求满足的过程日益个性化,上述良性循环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自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一种互相损害的关系。这同时弱化了自我和社区的力量。这种可怕的现实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市场越是把我们从社区的义务和影响中解放出来,个人的实际权利和自由反而会受到越严重的损害,当我们无法抵抗市场分化和征服的力量时,甚至对结果提出申诉的能力都没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瓦解社区的过程中,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我们还看到,很多人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视作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在很多方面,在很多层面上,冲动的社会都成功地把我们放在了对它而言最方便的位置上。
然而,现在我们的忍耐早已超过了上限。从市场撤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行为,不仅向社会表明我们没有获得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同时还宣布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唾手可得的。当我们远离市场的价值体系,社区的价值体系便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即便只是适度远离市场的控制,我们也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和真实感,这来源于我们与社区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这种快乐和真实感鼓励我们进一步扩大市场和自我的距离,于是我们和社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深入和持久。这种改善的过程虽然可能是缓慢的,但是改善的方向却是明确的——最终,恶性循环必将被打破。当然,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困难和挫折。由于几十年来人们的忽视,很多对健康社区而言非常必要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退化。此外,由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上下滑了一到两级,我们很可能缺乏远离市场的资金和能力。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社会联系的渴望以及对某种远大理想的追求仍然存在。只要我们能够获得一点点微小的机会和鼓励——在自我和市场之间制造出哪怕最微小的空间,我们将自我和社区重新连接的欲望便会像裂缝中的野草一样蓬勃地生长起来。一方面,野草会努力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另一方面,野草的根系则会深深地扎入冲动的社会的根基。
在基督教的教堂、犹太教的教会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里,我们每周都能看到这种野草般的欲望在蓬勃生长。在这些地方,人们寻找集体和社群的力量来重塑自我。在周五晚上举行的高中足球比赛中,那种原始部落般的能量表达着这种欲望。在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参与者乐观的情绪表达着这种欲望。在扶轮社的募捐活动中,人们对共同目标的肯定与信心表达着这种欲望。在关于公共土地使用的听证会上,人们强烈的情绪和诉求表达着这种欲望。在农民集市欢快的气氛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野草般的欲望。事实上,只要用心观察,便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着对社区、家庭等最基本社会结构的尊重及渴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些社会结构所代表的价值观——合作、滋养以及长期的承诺——能成为市场以及政治领域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对社区和社会连接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所缺乏的仅仅是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努力。一旦有了这样的努力,我们便可以清除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消除结构性的偏差,击退腐败,摒除品牌化的犬儒主义。我们对社区的渴望将引领我们重新回到一种更平衡的、更理性的社会定位中。
事实上,即便缺乏集体性的改革措施,重新回归社区的趋势也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蓬勃展开了。人们越来越偏爱各种“本地化”的商品和服务,这说明我们已经重新燃起对尼斯比特所说的“中介制度”(家庭、教堂、邻里、学校,以及其他小型的、本地化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对个人起支持作用,并能保护个人免受各种自然或人为的大规模力量的伤害)的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于最为恰当的地方——本地化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不仅社会关系具有最高的强度和频率,而且人们能以最具体的方式感受到这种关系,从而能最直接地体会到自我和社区重新连接的好处。圣母大学助理教授帕特里克·蒂宁是一位经典思想领域的专家,他这样写道:“要想理解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愿意为这种价值观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也就是说,既对过去的传承有义务感,又对未来的馈赠有责任感),首先必须在十分亲密的层面建立起这样的价值观。”在本地化的层面,我们能“感性和直观地体会到我们的行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人的行动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种感官上的联系”。同样,在本地化的层面上,我们最容易区分市场与非市场,因此也最容易建立和巩固非市场的价值观,比如真实、道德、质量以及社区。
尽管这种本地化的小型社会关系极为重要,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杰弗逊式的理想化社区形式(小型的、紧密的、亲近的)只是整个社会革新进程的一部分。今天,“本地”已经不能全面地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社区”的内涵也应变得更广,它应该考虑到国家甚至全球层面的问题,同时应该保持足够的多样性,以全面涵盖所有的人类经验和智慧。比如,我们应该复兴“工作”的理念,重新把工作视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连接,并把职场视作一种正当及重要的社区空间。拥有强大的工会以及高度团结的职场的时代或许一去不复返了,但如果说中产阶级还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那么劳动者就必须重新组建一个集体性的、高度连接的、有清晰自我意识并能表达自己声音的社区。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会接受各种新的社区形式,虽然其中某些形式(比如数字化社区)是本书某些章节的批判对象。我们应该清楚并坦诚地认识到,虽然数字化的网络环境可能成为社区复兴的渠道之一,但这样的网络环境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脸书和推特上的互动永远无法代替亲密的邻里会面、家长教师联谊会的筹款活动以及温馨的家庭聚餐。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某位政治领袖或某项政治议题也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履行了参与国家和州立政治事务的公民义务。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数字化社交网络已经完全吸收了效率市场的精神,因此它表现出所有效率市场的特征:强调快速回报、自我提升,并鼓励可随时抛弃的、不完整的互动形式——而这正是我们希望远离的。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数字世界的市场化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能将这些市场化元素分门别类,让每一位使用者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数字世界中市场化元素的存在(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让所有六年级以上学生接受必修的“技术教育”课程),那么这些科技完全有潜力成为社区的基石,也完全有可能用无限的可能性实现各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社会连接方式。毕竟,互联网产生的初衷便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聚集着各种渴望逃离主流文化、共享信息的人们。为什么这样的精神不能催生出一种公众交流的新渠道呢?事实上,网上乡镇会议已成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现象,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发展为一种规模更大的、更常规化的公众交流模式。
当然,不论数字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财富和灾难,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在非数字化的世界中,社区的发展仍存在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在美国的战后时期,在数字化技术尚未出现甚至尚未进入人们的想象世界时,美国的社区建设曾达到过惊人的高度,而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也都创造了辉煌的纪录。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线下”社区的重建方面,美国存在着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我们不应该让光怪陆离的数字世界迷乱双眼,更不应该听信数字世界的创造者们对数字社区的不断鼓吹。在数字世界以外的线下世界,存在着无数种建立有意义的重要社会连接的渠道,比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比如参加业余联盟的体育运动,比如多开展远离电子设备的家庭活动等。通过这些现实世界中的渠道,我们可以重新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个人与社区的正反馈关系。
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重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区。虽然重建较小规模的社区也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急需重新树立广泛的国家社区的理念。在目前陷入困境的庞大民主体系中,这反映了每个人作为公民的义务。虽然大型的国家社区可能缺乏本地社区那种亲密无间的、充满感情的氛围,但由于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力量才有可能解决,因此国家社区的重建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义务。只有国家社区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气候变化、创建新能源体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运行良好、具有适当凝聚力的国家社区才能为整个社会设定更远大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在本地层面以及个人层面重建社区的努力。只有国家社区的组织才能把各州和本地的各种改革努力进行政治化和经济化的包装。只有国家社区才能进行长期的有形投资和人力资源配置,并保证这些投资具有理性的、长远的目标。只有国家社区的组织才能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政府和个人之间建立长期互利的关系。
对许多深受品牌保守主义毒害、习惯于在任何情况下对政府保持无条件不信任的右派人士而言,重建国家社区的理念必然会为他们带来极大的挑战。然而,只要对我们目前的政治文化进行适度的改进(比如调低目前在政治立场上高度分化的媒体的声音),我们就有可能让保守派人士看到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能为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战略利益。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具建设性地参与政治,还能促成真正有意义的改变。而这样的变化完全可以促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正如今天很多实用主义的改革派保守人士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美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自上而下的大型改革计划(比如社会保险方面的改革、劳动力市场管理方面的改革以及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大规模投资的计划)能够重建个人的安全感,重塑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并让各种形式的社区在各种层面上获得发展与繁荣。
上述社会投资将为我们带来惊人的“回报率”。正如罗伯特·普特南及其他学者们所记载的那样,在战后的美国,社区的繁荣使公民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参与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志愿者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团队精神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力量让整个美国社会战胜了各种巨大的困难,赢得了各种艰巨的挑战。当然,今天的我们也许仍然能在大选的过程中看到这样的参与精神,在选举过程中,两党自上而下都表现出极强的参与精神(甚至是参战精神)。然而,我们急需建立的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参与氛围,政治领袖和选民都能以更低调、更有建设性、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参与政策的辩论与制定过程。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我们应该禁止极端的媒体声音煽动辩论中的公众情绪,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媒体应该被再次边缘化。
也许,目前美国社会中最有希望的迹象是对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以及公众对不平等现象持续上升的愤怒情绪。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区的理念和民主的制度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于缺乏经济方面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许多民众逐渐丧失了后物质主义的崇高理想,因此他们已经很难走出对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投资社区了。于是,在民众最需要社区支持的时候,社区却在迅速衰退,这个残酷的例子清楚地展示了良性循环是怎样变成恶性循环的。然而,收入不平等问题正是国家社区组织最有用武之地的领域之一。国家社区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重塑市场的公平和平衡,并且可以启动和推行上述各种改革。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可以把恶性循环重新推回良性循环的方向。当人们变得更有安全感,当社会真正让民众相信我们的社会确实在意每个人的利益和生活水平时,我们便会更愿意走出自我的狭小世界,将更多的时间贡献给我们的家庭、邻里和学校。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能够让民众相信,我们的经济并不完全是为富人和有政治权力的人服务的,这样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对美国梦以及对整个民主制度的信心。如今,两党的政治领袖都已经开始讨论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仅仅是这样的讨论已经能够向那些被社会忽视、对社会充满敌意的人群传递清晰的信号: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整个国家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时刻终于来了。
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的疲软、政治上的两党纷争、经济上的金融化倾向,由于选民日益将政治视作另一种消费和创造自我身份的渠道,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国家社区组织能够建立起来。然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一点破冰的可能性——两党之间的短暂妥协可能意味着更大尺度上的和解与合作。当然,必须承认,目前来看希望的火苗是十分微小的,然而这毕竟是一扇机会的窗口。透过这样的窗口,选民们有可能意识到冲动的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并认识到我们这个无法完成任何任务的政治体系是多么荒谬。通过创造必要的空间,我们可以客观地审视政治制度的表现有多么糟糕。因此,我们应该开始要求对这样的政治制度进行改善和重塑。即便某些不完美的元素不能完全消除,但我们的政治体系至少应该能履行它应有的功能——引导每位公民的个人利益,将个人的努力汇聚起来,创造出长期的、集体性的产出。
在此,我们将看到另一个良性循环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开始谈论真正的问题时,我们不再讨论死亡委员会 [33] 、大麻的合法性或者总统的出生证明,而开始讨论那些真正影响经济与社会命运的问题:我们讨论现代家庭面临的真正挑战,讨论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衰退,讨论创新的不当利用,讨论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竞选资金埋下的定时炸弹……当我们的政治文化能够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时,民众必然会更加关心、接受并认同这样的政治文化。因为这些问题是超越了党派界限的真正重要的问题。由于政治立场的分裂,我们国家的政治地图上镶满了红色和蓝色的补丁,我们可以为这样的现实感到遗憾,然而这样的事实却无法阻止我们寻找和创造共同的价值。这些共同的价值应该穿透我们在立法上的分歧,重申我们对公正、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共同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关闭极端媒体的声音,将击退两党无法合作的恶性假设,重新发现共同利益所在,重塑中立的政治阵营。也许,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逐渐认识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偏左或偏右,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远比我们的不同点更多且更重要。
至此,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在政治领域,这样的良性循环在其他领域同样可以建立起来;其他的全国性政治议题也同样可以用类似的自上而下,同时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的政治机器已经陷入了国家层面上的失灵状态。推行碳排放税的努力受到了金融化的政治体系的严重阻碍,而正是这种金融化的政治体系让能源行业规避了改变的风险——这是典型的冲动的社会的弊病。与此同时,在地区和州的层面上却出现了各种支持碳排放税的运动。只要有合适的组织和引导,这种地区层面的运动完全可以转化成全国性的运动。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气候变化——如干旱、山火、沙尘暴等——影响较大,地区性的环保运动已经成功转化成了有建设性的州政策。这些州政策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其他州的范本,并有望最终成为联邦政府环保政策的范本——过去马萨诸塞州的医疗系统模式就逐渐进化成了全国医疗系统的统一模式。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一个由各地环保积极分子(其中很多成员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组成的、快速成长的国家社区通过采取一种全新的“职业”策略,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广泛的政治压力。这种策略目前在成熟的绿色团体中已经不多见了。其中影响最广的例子之一是:在这一国家社区组织的运作下,超过75 000名环保积极人士随时准备抵制Keystone XL项目。该项目是一个输油管道项目,该管道主要用于把将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的石油从加拿大的油砂蕴藏地运往美国。在这一全国性抵制活动的威胁下,奥巴马政府最终搁置了对该项目的批准。
也许,这种自上而下,同时自下而上的方式在教育领域最能发挥作用。在冲动的社会的影响下,美国的教育业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和许多工业化程度不如我们的国家相比,美国学龄儿童的学业表现令人十分失望,这样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振兴经济以及取得长期经济繁荣的能力。然而,在教育领域存在着大量民众参与、改革提高以及社区建设的机会,这方面的潜力还远远未被完全开发。在国家层面,联邦政府试图在各州的公立学校中推行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虽然很多地区对统一的国家标准持怀疑的态度,但共同核心运动还是赢得了比较广泛的民意支持。在地区层面,改革者们正在实验各种新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方法,比如特许学校 [34] ,比如一种让学生在家收看在线教学录像,然后在学校当堂完成作业的“反转型”教学模式。当然,在这些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中,有不少仍然具有很大的争议。然而,这些实验和改革措施的存在反映了一种全民参与、自己动手的热情与精神。这种自己动手的热情与精神曾经是整个美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鼓励,这种精神完全可以再次盛行起来。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教育可能是最能激励个人积极参与并采取实际行动的领域。教育常常是成年人走出家庭和邻里的怀抱、正式参与社区活动的第一个机会。教育也常常是我们参与政府活动的第一个机会:当我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不满时,我们往往有很强的动机要做出实际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是为添置教室的教学设备而举行的筹款活动,可能是呼吁提高本地征税额度的政治宣传活动,也可能是竞争学校董事会成员席位的竞选活动。我的朋友玛西发现了这样的规律:教育为富有野心的个人提供了一条回馈社区的清晰而平坦的途径。人类天生具有回馈社区与社会的欲望。参与社会活动、创造某种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东西的欲望与人类其他更低等、更受蜥蜴脑控制的欲望一样自然。我们缺乏的不是这方面的本能和愿望,我们缺乏的是时间、空间以及正确的鼓励和引导。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提供这样的时间、空间以及鼓励和引导。并且这种坚持应该来自我们的内心。当我的朋友玛西谈论她放弃高薪工作而成为一名教师的决定时,她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当时她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不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要寄希望于什么样的人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呢?”
冲动的社会不会鼓励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一味追求高收益率、被商业利益的永动机所驱动的社会中,我们永远在寻找着更完美、更个人化的满足机会,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任何超出短期自我利益以外的现实情况。当我们走出短期自我利益的狭隘世界,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仅为己,我为何物?若非此时,更待何时?”我们事实上否认了市场的逻辑,并坚持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更古老的价值体系。在这套更古老的价值体系中,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为某种更伟大的目标奋斗和服务时,个人的自由和权力才能真正实现。更重要的是,通过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便迈出了反叛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拒绝了支持冲动的社会存在的核心理念——短视的、自我沉醉的、破坏性的现状是整个社会的最优情况。这条冲动的社会的核心“真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当然,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鼓起勇气来回答这个问题。
[1] Book 1, chapter 8, http://econlib.org/library/Smith/smWN3.html#I.8.35.
[2] Book 2, chapter 2, http://econlib.org/library/Smith/smWN7.html#II.2.94.
[3] “The Real Adam Smith Problem: How to Live Well in Commercial Society,”The Philosopher’s Beard (blog), Sept. 12, 2013, http://www.philosophersbeard.org/2013/09/the-real-adam-smith-problem-how-to-live.html.
[4] Peter S. Goodman, “Emphasis on Growth Is Called Misguided,”New York Times ,Sept 22,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9/23/business/economy/23gdp.html?ref=business&_r=0.
[5] 为了限制对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戴利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对原材料课以重税,以限制经济活动过度耗能的问题;二是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方式降低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戴利看来,最富裕阶层的收入与中位数劳动者的收入之比永远不应该超过100∶1。戴利认为,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种合理的经济模型,这种经济模型“能够对真正的创造和贡献进行奖励,而非不断扩大特权阶级的特权”。
[6] Herman E. Daly, “A Steady-State Economy,” text delivered to U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pril 24, 2008.
[7] Bill McKibben, “Breaking the Growth Habit,”Scientific American , April 2010, http://www.scientifi camerican.com/article.cfm?id=breaking-the-growth-habit&print=true.
[8] Coral Davenport, “Industry Awakens to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New York Times ,Jan. 23,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1/24/science/earth/threat-to-bottom-line spurs-action-on-climate.html?hp.
[9] Goodman, “Emphasis on Growth Is Called Misguided.”
[10] Gregg D. Polsky and Andrew C. W. Lund, “Ca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form Cure Short-Termism.”
[11] Susanne Craig, “Cuomo, Frank Seek to Link Executive Pay, Performance,”Wall Street Journal , March 13, 2009,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23690181841413405?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FSB1236901818 41413405.html#mod=testMod.
[12] Gretchen Morgenson, “An Unstoppable Climb in C.E.O. Pay,”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6/30/business/an-unstoppable-climb-in ceo-pay.html?pagewanted=all.
[13] Diane Stafford, “High CEO Pay Doesn’t Mean High Performance, Report Says,”Kansas City Star , Aug. 28, 2013, http://www.kansascity.com/2013/08/28/4440246/high-ceo-pay doesnt-mean-high.html.
[14] Brian Montopoli, “Ronald Reagan Myth Doesn’t Square with Reality,” CBSNews,Feb. 4, 2011, http://www.cbsnews.com/news/ronald-reagan-myth-doesnt-square-with reality/.
[15] Peter Beinart, “The Republicans’ Reagan Amnesia,”The Daily Beast , Feb. 1, 2010,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0/02/01/the-republicans-reagan-amnesia.html.
[16] 几年前,《每日野兽》网站的皮特·贝纳特曾说:“为了让今天的茶党支持者们能够充分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必须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来概括一下当时的情况,那就是:里根政府确实曾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来支持靠政府运营的医疗福利系统。”
[17] 关于这一点,并未完全成功的“公司可持续性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18] 德拉古是一位古代雅典执政官,以严刑峻法著称。——译者注
[19] Richard W.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20] Evan Pérez, “First on CNN: Regulator Warned against JPMorgan Charges,” CNN,Jan. 9, 2014, http://www.cnn.com/2014/01/07/politics/jpmorgan-chase-regulators prosecutors/.
[21] 进步时代是指1890—1920年间,美国社会涌现大量进步改良措施的时段。——译者注
[22]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23] George F. Will, “Time to Break Up the Big Banks,”Washington Post , Feb. 9, 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eorge-will-break-up-the-big-banks/2013/02/08/2379498a-714e-11e2-8b8d-e0b59a1b8e2a_story.html.
[24]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25]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26] Liz Benjamin, “What Would Cuomo Do to Get Public Financing?”Capital New York , Jan. 20, 2014, http://www.capitalnewyork.com/article/albany/2014/01/8539039/what-would cuomo-do-get-public-f inancing.
[27] Liz Kennedy, “Citizens Actually United: The Bi-Partisan Opposition to Corporate Political Spending and Support for Common Sense Reform,” Demos, Oct. 25, 2012, http://www.demos.org/publication/citizens-actually-united-bi-partisan-opposition-corporate-political spending-and-support.
[28] Chris Myers, “Conservatism and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The Two Aren’t Mutually Exclusive,”RedState , April 24, 2012, http://www.redstate.com/clmyers/2013/04/24/conservatism-and-campaign-f inance-reform/.
[29] David Brooks, “The Opportunity Coalition,”The New York Times , Jan 30, 2014.
[30] “2013 Report Card for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http://www.infrastructurereportcard.org/.
[31] In Robert Frank, The Darmn Economy: Liberty, Competition, and Common Good .
[32] Brooks, “The Opportunity Coalition.”
[33] “死亡委员会”是指在奥巴马医疗改革的过程中有权决定哪些人能够获得医疗保险的官僚机构。民众对这个机构及整个医改项目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些官僚机构能够决定哪些人获得医保,哪些人无法获得医保,掌握着民众的生死大权。——译者注
[34] 美国的特许学校是一类介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学校,特许学校可以像公立学校一样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但不必完全遵照公立学校的教学大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教学内容和方法。——译者注
每一本书都是合作的结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尤其需要感谢很多人对我的帮助。本书涉及很多相当复杂的议题,甚至很多议题颇富争议性。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这些问题,我与许多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他们不仅慷慨地向我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还体贴地帮我考虑如何将这些问题嵌入我在整部书中想要描述的大主题中。在此我想特别感谢以下专家的帮助:Dean Baker、Bill Bishop、Robert Bixby、Robert Boyd、Ralph Brown、Keith Campbell、Daniel Callahan、Hilarie Cash、Amitabh Chandra、Jonathan Cohen、Tyler Cowen、Richard Curtain、Richard Davies、Michael X. Delli Carpini、Jake Dunagan、Judith Feder、Andrew Haldane、Dacher Keltner、Bill Lazonick、George Loewenstein、Michael Mandel、Sam McClure、Todd Miller、Manoj Narang、Paul Piff、Clyde Prestowitz、Peter Richerson、Judy Samuelson、Walker Smith、Evan Soltas、Dilip Soman、Kenneth Stone、Richard Thaler,以及Eric Tymoigne。此外,我还想特别感谢帮我通读本书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人,他们是:Matt Roberts、Molly Roberts、Karen Dickinson、Nina Miller、Claire Dederer、Fred Moody、Paul Bravmann、Susan Kucera、Ralph Brown、Bill Lazonick以及Johann Hari。另外还有人与我分享了他们与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手故事,这些内容都是本书的珍贵素材,在此尤其需要感谢Brett Walker和Marcie。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感谢布卢姆茨伯里出版公司的以下工作人员:George Gibson、Laura Keefe、Nikki Baldauf、Rachel Mannheimer、Summer Smith,特别是我的编辑Anton Mueller。如果没有他们的智慧和好奇心,以及愉快地在深夜和周末加班的精神(后者才是最主要的),本书一定无法与大家见面。
最后,我想感谢那些在本书的写作(以及重写)过程中向我提供鼓励、支持以及餐饮的人,他们包括:整个Dickinson部落;Chris Brixey与Andrea Brixey夫妇;Eurosports的Eric和Ben;Luke、Colin和Luis;Stephen Sharpe以及“A Book For All Seasons”书店;Homefires的Linda和Jake Schocolat的Damian和Susie;Sage Mountain的Susan;Good Mood Food的Kurt和Nadine;Roy Gumpel;Susan Garner;以及某位骑双人自行车的人。当然,最后我必须感谢对我而言最重要的Hannah和Isaac,如果我的心是一个圆规,你们便是这圆规的双脚。
Alder, Nathan. New Lifestyles and the Antinom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Alexander, Jennifer Karns. The Mantra of Efficiency: From Water Wheel to Social Contro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2008.
Baker, Dean.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Making Markets Progressive .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11.
Baker, Dean, and Thomas Frank. Plunder and Blund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bble Economy . San Francisco: PoliPoint Press, 2009.
Bell, Danie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Bellah, Roberts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Bevan, Tom, and Carl Cannon. Election 2012: The Battle Begins . The Real ClearPolitics Political Download. 2011.
Bishop, Bill.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Boston: Houghton Mif f lin, 2008.
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Bradsher, Keith. High and Mighty: SUVs —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Vehicles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Braudel, Fernand.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ian Reynold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Brown, Clair, and Greg Linden. Chips and Change: How Crisis Reshape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Driving Productivity, 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 . Boston: Digital Frontier Press, 2012.
Burnham, Terry, and Jay Phelan. Mean Genes: From Sex to Money to Food Taming Our Primal Instincts . New York: Penguin, 2000.
Calder, Lendol.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Carr, Nicholas.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W. W.Norton, 2011.
Chandler, Alfre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oates, John. The Hour between Dog and Wolf: Risk Taking, Gut Feelings and the Biology of Boom and Bust .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2.
Cowen, Tyler.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Dutton, 2013.
———.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 New York: Dutton, 2011.
Davis, Gerald.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ionne, E. J. Our Divided Political Heart: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Idea in an Age of Discontent .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
Donaldson-Pressman, Stephanie, and Robert M. Pressman. The Narcissistic Fami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 New York: Macmillan, 1994.
Fishman, Charles. The Wal-Mart Effect: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Really Works —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the American Economy .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Frank, Robert. The Darwin Economy: 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Frank, Robert,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Frank, Thomas, and Matt Weiland, eds. Commodify Your Dissent: The Business of Culture in the New Gilded Age .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Friedman, Milto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Hacker, Jacob S.,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Hammond, Phillip E. Religion and Personal Autonomy: The Third Disestablishment in America .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2.
Hirschman, Albert.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rowitz, Daniel. Anxieties of Af f luence: Critiques of American Consumer Culture, 1939–1979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4.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ckson, Tim. Inside Intel: Andy Grove and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hip Company . New York: Penguin, 1997.
Kanigel, Robert. The One Best Way: Frederick Taylor and the Enigma of Efficiency . New York: Viking, 1997.
Katona, George et al. Aspirations and Af f lu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Kling, Arnold. Crisis of Abundance: Rethinking How We Pay for Health Care . Washington,DC: Cato Institute, 2006
Krippner, Greta.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Lasch, Christopher.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Levins, Richard. Willard Cochrane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0.
Lichtenstein, Nelson. The Retail Revolution: How Wal-Mart Created a Brave New World of Business . New York: Picador, 2009.
Lichtenstein, Nelson, ed. Wal-Mart: The Face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 New York:The New Press, 2006.
Lindsey, Brink. The Age of Abundance: How Prosperity Transformed America’s Politics and Culture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Lowenstein, Roger. When Genius Failed: The Rise and 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Lynch, Michael. True to Life: Why Truth Matters . Cambridge, MA: Bradford Books, 2004.
Marin, Peter. Freedom and Its Discontents: ReAections on Four Decades of American Moral Experience . South Royalton, VT: Steerforth, 1995.
Marsh, Peter, and Peter Collett. Driving Passi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Car . Boston: Faber &Faber, 1986.
Messick, David M., and Roger M. Kramer,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hip: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McCloskey, Deirdre. The Bourgeois Virtues: 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Mokyr, Joel.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orozov, Evgeny.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Noah, Timothy. The Great Divergence: 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
Nordhaus, Ted, and Michael Shellenberger, Break 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 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Boston: Houghton Mif f lin, 2007.
Packard, Vance. The Hidden Persuaders .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58.
———. The Waste Makers .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4.
Pelfrey, William. Billy, Alfred, and General Motors: The Story of Two Unique Men, a Legendary Company, and a Remarkable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
Phillips, Kevin.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 Penguin, 2006.
Putnam, Robert.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Rappaport, Alfred. Saving Capitalism from Short-Termism: How to Build Long-Term Value and Take Back Our Financial Future . New York: McGraw-Hill, 2011.
Sennett, Richard.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hiller, Robert. Irrational Exuberance .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Slade, Giles. Made to Break: Technology and Obsolescence in Americ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2.
Smith, Merrit Roe, and Leo Marx, eds.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Sunstein, Cass R. Republic. com 2.0: Revenge of the Blog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Oliver Wendell Holmes Lectur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aler, Richard H. Quasi R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Thaler, Richard, and Cass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urkle, Sherry.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Twenge, Jean, and W. Keith Campbell. The Narcissism Epidemic: 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 . 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Tymoigne, Eric., and L. Randall Wray. The Rise and Fall of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 Minsky’s Half Century from World War Two to the Great Recession . Rout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Finance and Stability. Oxford: Routledge, 2013.
Weiss, Eugene H. Chrysler, Ford, Durant and Sloan: Founding Giants of the American Automotive Industry .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3.
Wood, Michael, and Louis Zurcher Jr.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modern Self: A Computer Assis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sonal Documents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Selected Articles: Abramowitz, Alan. “Don’t Blame Primary Voters for Polarization.”The Forum: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Selection 5, no. 4 (2008).
Abramowitz, Alan, Brad Alexander, and Matthew Gunning. “Incumbency, Redistricting,and 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 in U.S. House Elections.”Journal of Politics 68, no. 1(Feb. 2006): 75–88.
Abramowitz, Alan, and Morris P. Fiorina. “Polarized or Sorted? Just What’s Wrong with Our Politics, Anyway?”American Interest , March 11, 2013.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3. Doi: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 article.cfm?piece=1393.
Auletta, Ken. “Outside the Box.”New Yorker , Feb. 3, 2014.
Baker, Dean. “The Productivity to Paycheck Gap: What the Data Show,” brief ing paper,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pril 2007. http://www.cepr. net/documents/publications/growth_failure_2007_04.pdf
———.“The Run-Up in Home Prices: Is It Real or Is It Another Bubble?” brief ing paper,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ugust 2002, http://www. 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housing_2002_08.pdf.
Beinart, Peter. “The Rise of the New New Left.”Daily Beast , Sept. 12, 2013. Doi: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9/12/the-rise-of-the-new-new- left.html.
Brooks, David. “The Opportunity Coalition.”New York Times , Jan. 30, 2014, A27.
Cecchetti, Stephen G., and Enisse Kharroubi.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Band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381, July 2012. Accessed August 4, 2013. Doi: http://www.bis.org/publ/work381.pdf.
Cobb, Clifford, Ted Halstead, and Jonathan Rowe. “If the GDP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Atlantic , Oct. 1995. Accessed November 7, 2012. Doi: http:// www.theatlantic.com/past/politics/ecbig/gdp.htm.
Cutler, David, and Mark McClellan. “I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cine Worth It?”Health Affairs 2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11–29.
Daly, Herman E. “A Steady-State Economy.” Text delivered to U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pril 24, 2008.
Davidson, Adam. “Making It in America.”Atlantic , Dec. 20, 2011.
Duhigg, C. “How Companies Learn Your Secrets.”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Feb. 16, 2012,MM30.
Drum, Kevin. “You Hate Me, Now with a Colorful Chart!”Mother Jones , Sept. 26, 2012.Accessed March 14, 2013. Doi: 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2/09/you hate-me-now-colorful-chart.
Easterbrook, Gregg, “Voting for Unemployment: Why Union Workers Sometimes Choose to Lose Their Jobs Rather Than Accept Cuts in Wages.”Atlantic , May 1983.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13. Doi: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 docs/issues/83may/eastrbrk.htm.
Edsall, Thomas B. “The Obamacare Crisis.”New York Times , Nov. 19, 2013. Doi: http://www.nytimes.com/2013/11/20/opinion/edsall-the-obamacare-crisis. html?pagewanted=1&_r=2&smid=tw-share&&pagewanted=all.
Field, Alexander J.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U.S. Productivity Growth.”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 no. 3 (2008): 677.
———.“The Origins of 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Golden Age.”Cleometrica 1, no. 1 (April 2007): 19, 20.
Fisher, Richard. “Ending ‘Too Big to Fail’: A Proposal for Reform before It’s Too Late(with Reference to Patrick Henry, Complexity and Realit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to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public. Washington,DC, January 16,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 2013, Doi: http://www.dallasfed.org/news/speeches/f isher/2013/fs130116.cfm.
Fleck, Susan et al.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Monthly Labor Review , January 2011. Accessed October 13, 2012. Doi: http:// www.bls.gov/opub/mlr/2011/01/art3full.pdf.
FRED Economic Dat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Graph: Corporate Prof its after Tax(without IVA and CCAdj) (C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March 13, 2014. Doi: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graph/?g=cSh.
Fullerton, Robert. “The Birth of Consumer Behavior: Motivation Research in the 1950s.”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Bienni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Marketing, May 19–22, 2011.
Good, James A., and Jim Garrison. “Traces of Hegelian Bildung in Dewey’s Philosophy.” In John Dewe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 edited by Paul Faif ield.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0. Available at Google Books.
Hagel, John et al. “The 2011 Shift Index: Measuring the Forces of Long-Term Change.”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2011.
Haldane, Andrew. “Financial Arms Races.” Essay based on a speech given at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Berlin, April 14, 2012.
———.“The Race to Zero.” Speech given a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Sixteenth World Congress, Beijing, China, July 8, 2011.
Haldane, Andrew G., and Richard Davies. “The Short Long.” A speech delivered at Twenty Ninth Société Universitaire Européene de Recherches Financières Colloquium: New Paradigms in Money Finance, Brussels, May 2011. http:// 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speeches/2011/ speech495.pdf.
Haveman, Ernest, “The Task Ahead: How to Take Life Easy.”Life , Feb. 21, 1964. Available at Google Docs.
Heller, Nathan. “Laptop U: Has the Future of College Moved Online?”New Yorker ,May 20, 2013.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3/05/20/130520fa_fact_
heller?currentPage=all.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no. 4(October 1976): 305–60.
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Brent Neiman. “Declining Labor Shares and 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154,June 2012. Accessed October 4, 2013. Doi: http:// www.nber.org/papers/w18154.
Katz, Daniel.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 — Or —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62, no. 909 (2013): 965.
Knowles, Joh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Daedalus 106, no. 1 (Winter 1977).
Krueger, Alan B.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Lecture delivered at “Learning and Labor Economics” Conference at Oberlin College, April 26, 2013. Accessed August 14, 2013.Doi: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 iles/docs/oberlin_+nal_revised.pdf.
Krugman, Paul. “Def ining Prosperity Down.”New York Times , July 7,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08/opinion/krugman-defi ning-prosperity- down.html?src=recg.
Kuchler, Hannah. “Data Pioneers Watching Us Work.”Financial Times , February 17,2014.
Lazonick, William.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Innovation & Growth 2011.
Lazonick, William, and Mary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conomy and Society 29, no. 1 (Feb. 2000): 19.
Loewenstein, George, “Insuf f icient Emotion: Soul-Searching by a Former Indicter of Strong Emotions.”Emotion Review 2, no. 3 (July 2010): 234–39.http://www.cmu.edu/dietrich/sds/docs/loewenstein/Insuf f icientEmotion. pdf.
Lynd, Robert S. “The People as Consumers.”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n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with a Foreword by Herbert Hoover , 857–911.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 Accessed May 11, 2013. Doi:http://archive.org/stream/recentsocialtren02pres rich#page/867/mode/1up.
Madrigal, Alexis C. “When the Nerds Go Marching In.”Atlantic , Nov. 16, 2012. Accessed Sept. 27, 2013. Doi: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 archive/2012/11/when-the nerds-go-marching-in/265325/?single_page=true.
Mankiw, Gregory N.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 3 (Summer 2013). http://scholar.harvard.edu/f iles/ mankiw/f iles/defending_the_one_percent_0.pdf.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96.
McGaughey, William Jr. “Henry Ford’s Productivity Less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22, 1982. Accessed March 11, 2012. Doi: http://www.csmonitor. com/1982/1222/122232.html.
McKibben, Bill. “Breaking the Growth Habit.”Scientific American , April 2010. Accessed May 8, 2012. Doi: http://www.scientif icamerican.com/article. cfm?id=breaking-the growth-habit&print=true.
———.“Money ≠ Happiness. QED,”Mother Jones , March/April 2007.
McLean Bethany, and Joe Nocera. “The Blundering Herd.”Vanity Fair , Nov.2010.http://www.vanityfair.com/business/features/2010/11/f inancial-crisis- excerpt–201011.
Murphy, Kevin J. “Pay, Politic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edited by Alan S. Blinder, Andrew W. Lo, and Robert M. Solo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Murphy, Tom. “An Angel and a Brute: Self-Interest and Individualism in Tocqueville’s America.” Essay for preceptorial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 St. John’s College, Santa Fe,NM, Summer 1985. Accessed June 8, 2013. Doi: http://www.brtom.org/sjc/sjc4.html.
Noah, Timothy, “The United States of Inequality,” Salon, Sept. 12, 2010.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13. Doi: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 the_great_ divergence/features/2010/the_united_states_of_inequality/the_ great_divergence_and_the_ death_of_organized_labor.html.
Parker, Kathleen. “A Brave New Centrist World.”Washington Post , Oct. 15, 2013. Accessed November 1, 2013. Doi: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kathleen-parker-a brave-new-centrist-world/2013/10/15/ea5f5bc6–35c9–11e3-be86–6aeaa439845b_story.html.
Polsky, G., and Lund, A. “Ca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form Cure Short-Termism?”Issues in Governance Studies 58 (March 2013).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urinton, Edward. “The Eff icient Home.”Independent 86–87 (May 15, 1916): 246–48.Available in Google Docs.
Rappaport, A. et al. “Stock or Cash: The Trade-Offs for Buyers and Seller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Nov.–Dec. 1999, p.147. Accessed July 13, 2013.Doi: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law/pg/offer/ llm/iel/mas_sample_lecture.pdf
Reguly, Eric. “Buyback Boondoggle: Are Share Buybacks Killing Companies?”Globe and Mail , Oct. 24, 2013.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 Doi: http://www. 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rob-magazine/the-buyback-boon- doggle/article15004212/.
Rowe, Jonathan. “Our Phony Economy.”Harper’s , June 2008. Accessed November 8, 2012.Doi: http://harpers.org/print/?pid=85583.
Schoetz, David. “David Frum on GOP: Now We Work for Fox.” ABCNews, March 23, 2010.Accessed November 18, 2013. Doi: http://abcnews.go.com/ blogs/headlines/2010/03/david frum-on-gop-now-we-work-for-fox/.
Senft, Dexter. “Impact of Technology of the Investment Proces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CFA Institute Seminar “Fixed-Income Management 2004.” CFA Institute, 85–90.
Smaghi, Lorenzo Bini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The Paradigm Shif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Speech at the Nomura Seminar.Kyoto,April 15, 2010. http://www.ecb.europa.eu/press/key /date/2010/ html/sp100415.en.html.
Smith, Hedrick. “When Capitalists Cared.”New York Times , Sept. 2, 2012, A19.
Stokes, Bruce. “Europe Faces Globalization — Part II: Denmark Invests in an Adaptable Workforce, Thus Reducing Fear of Change.”YaleGlobal , May 18, 2006.
The Economist. “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 Jan. 19, 2013. Accessed January 23, 2913. Doi: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69570-growing number-american-companies-are-moving-their- manufacturing-back-united.
White, Michelle J., “Bankruptcy Reform and Credit Card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no. 4 (Fall 2007): 175–99.
Will, George F. “Time to Break Up the Big Banks.”Washington Post , Feb. 9, 2013. Accessed September 2, 2103. Doi: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opinions/george-will-break-up the-big-banks/2013/02/08/2379498a–714e–11e2–8b8d-e0b59a1b8e2a_story.html.
Wohlfert, Lee. “Dr. John Knowles Diagnoses U.S. Medicine.”People , May 6, 1974. Accessed April 11, 2013. Doi: http://www.people.com/people/archive/ article/0,20064026,00.html.
Wolfe, Thomas. “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New York Magazine ,August 23, 1976.
Wood, Allen W. “Hegel on Education.” In Philosophy as Education , edited by Amélie O.Ror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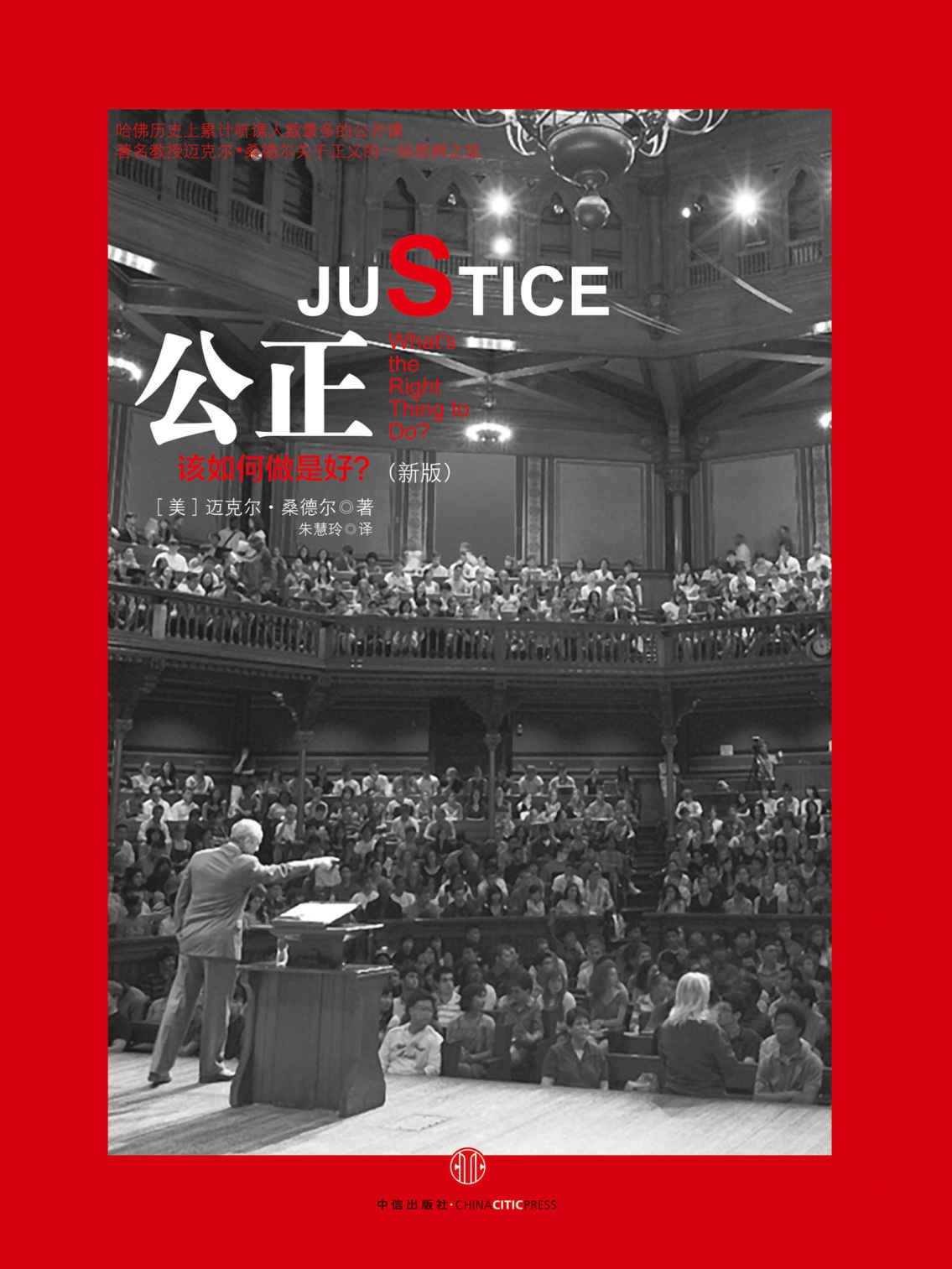
2004年夏,飓风“查理”从墨西哥湾咆哮而出,横扫佛罗里达,直至大西洋。此次飓风夺去了22条生命,并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同时,它还引发了一场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
在奥兰多市内的一个加油站,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当时正值8月中旬,因为停电不能使用冰箱和空调,所以人们别无选择,而只能购买高价冰块。飓风刮倒了很多大树,使得链锯的需求量猛增;很多住宅的屋顶也急需修葺。然而,从屋顶上清理掉两棵树竟然也要付给施工方2.3万美元。平时在商店里卖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此时却涨到了2 000美元。一个77岁老妪和她年迈的丈夫以及残疾的女儿在飓风中逃出家门,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但此时每个房间的单日住宿价格已从40美元飙升到了160美元。 [2]
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今日美国》(USA Today)的一个头条报道如此命名:“刚送走飓风,又迎来秃鹰”。当一个居民得知他需要花费10 500美元才能将一棵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道:“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同意此种说法:“有些人的灵魂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在别人遭受飓风灾害时趁机发财。” [3]
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在此次飓风之后,总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两千多件投诉,并有人通过诉讼获得了赔偿。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的一家“戴斯酒店”(Days Inn)由于索价过高,被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以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4]
然而,当克里斯特着手执行反价格欺诈法时,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该法律并不适用这种情况,而人们的愤怒也是误解所致。只有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才会认为商品交换应当根据基于传统或物品固有价值的“正当的价格”来进行。在当下的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正当的价格”在商品交换中已不复存在。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一位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价格欺诈”的说法“能够有效地煽动人们的情绪,在经济学上却站不住脚。这是个非常混乱的概念,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干脆不予理会。索维尔在《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 (1) 上撰文,试图解释“‘价格欺诈’是如何让佛罗里达居民受惠的”。索维尔写道:“当价格明显高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价位时,人们就会指责这是价格欺诈。然而,人们恰好习以为常的价格水平,并非在道德上就是不可侵犯的。普通价格水平与在市场条件变化时—比如遭遇飓风—所产生的价格相比,并没有特殊性,也并非更加公平。” [5]
索维尔认为,冰块、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以及汽车旅馆的过高价格,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飓风受灾地区提供最急需的物品和服务。当佛罗里达居民在炎热的8月遭遇停电的时候,如果冰块卖到10美元一袋,那么冰块制造商们就会发现这值得他们生产和运输更多的冰块。索维尔解释道,这些价格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它们只是反映出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同意的价值。 [6]
杰夫·雅各比(Jeff Jacoby)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位支持自由市场的评论家,他以类似的理由反对反价格欺诈法:“根据市场所产生的价格索价,并不是欺诈,也不是贪婪或无耻之举,而只是物品和服务在自由社会中获得分配的方式。”雅各比也承认:“价格暴涨确实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被致命的飓风严重扰乱生活的人们而言。”然而公众的愤怒并不能成为干涉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那看起来过分的价格能够刺激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必需品,“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的危害”。由此,他的结论是:“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而让他们自由地开展业务却可以。” [7]
总检察长克里斯特(一名共和党人,后来被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在《坦帕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比如当人们逃命时,或者在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日用品时,被索要过高价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 [8] 克里斯特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过高的”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自由交换: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情形。在正常的自由市场情形中,有意愿的购买者自行选择进入市场,并遇到有意愿的销售者,此时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而在紧急状况中,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 [9]
“查理”飓风之后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引发了一些与道德和法律相关的棘手问题:物品和服务的销售商利用一场自然灾害,根据市场需求随意定价,这是否是不正当的?如果不正当,那么法律应当做些什么呢?政府是否应当禁止价格欺诈—即使这样做干涉了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交易自由?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法律应当如何制定,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公正的问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必须探索公正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护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使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公正的方式。
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有关福利,另一种有关自由。首先,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市场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福利。(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的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
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拥护者们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认为,社会整体福利并不是由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而真正地达到的。即使高价能够促进更多的商品供应,这一益处也会被高价给那些无法支付得起的人们所带来的负担抵消。对于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的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而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然而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带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
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拥护者们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被迫的购买者们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风,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要评估这些关于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
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诸多公众对于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都源自于一种直觉的反应,而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常被看做是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 [10]
然而,对于反价格欺诈者们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而感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公正的愤怒。
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在他的评论中却暗含着下列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的论证:
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它还与公民德性相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良好的社会会凝聚在一起。人们之间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最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因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而一个良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之。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最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社会肯定了那种为了群体善而共同牺牲的公民美德。
承认德性论证的道德力量,并非就是认为它必须总是超越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个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认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即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它也与德性相关—它涉及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
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们—发现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不应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它并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否能真正地自由选择,也并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
相比之下,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们不是对这些事物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
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当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感到愤慨;我们认为,那种在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感到担忧。
这一困境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努力推进其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德性观念保持中立,以使公民们能够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了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公正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良善生活的各种问题。
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们—从18世纪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那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公正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最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他自己的关于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
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公正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则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促进当代政治中—并非在哲学家们之间,而是在普通人之间—关于公正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景象。的确,我们的大多数争论都与促进繁荣和尊重个人自由有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而,或与之相冲突的是,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它们涉及什么样的德性值得尊重和奖赏,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推进的。尽管我们致力于推进繁荣和自由,我们也不能全然摆脱关于公正的道德评判。那种认为公正涉及德性和选择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关于公正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
在某些事情上,德性与荣誉问题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加以否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最近关于谁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the Purple Heart) (2) 的争论。自1932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将这一奖章授予那些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的士兵。除了能带来荣誉之外,这枚奖章还能使获得者在老兵医院中享有诸多特权。
自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开战以来,越来越多的老兵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接受治疗。其症状包括连续做噩梦、极度抑郁以及有自杀趋向。据报道,至少有30万老兵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支持者们认为,老兵们同样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既然心理上的创伤至少与身体上的创伤一样使人衰弱,那么,忍受这种伤痛的老兵们就应当获得这一勋章。 [11]
五角大楼的顾问团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于2009年宣布,紫心勋章只授予那些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士兵。那些精神失调或心理上受到伤害的老兵,即使有资格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医学治疗和残疾补助,也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由敌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它们很难得到客观的诊断。 [12]
五角大楼的决定正确吗?如果我们仅看这些理由的话,它们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最普通的、紫心勋章所认可的创伤就是近距离爆炸所造成的鼓膜穿透。 [13] 与子弹和炸弹有所不同,这类爆炸并不是敌方战术故意要造成的伤害和牺牲。它们(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是战争行为所产生的、损伤性的副作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比断肢更难以诊断,然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更加严重和持久。
正如关于紫心勋章的广泛争论所揭示的,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枚奖章的意义及其所尊重的德性。那么,与此相关的德性是什么呢?与其他部队奖章不同,紫心勋章尊敬牺牲,而非勇敢。它不要求要有英雄的行为,只需要由敌人造成的伤害;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伤害应当被奖励。
一个叫做“紫心勋章骑士团”的老兵俱乐部反对由于心理上的创伤而授予这一奖章,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贬低”这份荣誉。该团体的发言人声明:“流血”应当是一项必要条件。 [14] 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流血的创伤就不算数。然而,支持将心理创伤包括在紫心勋章奖励范围之内的前海军上校泰勒·布德罗(Tyler E.Boudreau),为这一争论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析。他将这里的反对之声归咎于军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种强调坚强意志的文化,同样也导致人们对‘战争暴力能够伤害最健康的心灵’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令人悲哀的是,只要我们的军事文化对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还存有一种哪怕暗中的蔑视,那么,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老兵们就不可能得到紫心勋章。” [15]
因此,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并不只是一种如何界定伤害之真实性的医学或临床上的争论。此争论的核心在于各种不同的关于道德品格和士兵勇气的观念。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流血的创伤才应当算数的人们相信,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出一种不值得尊敬的性格上的软弱;而那些认为心理创伤也应当算数的人们则反驳说,那些受到长期性的心理创伤和严重抑郁症所折磨的老兵们,与那些失去一只胳膊的老兵们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牺牲同样确凿无疑,同样光荣。
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阐明了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伦理逻辑。如果我们不询问一枚军队奖章尊敬的德性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一奖章。并且,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评价不同的有关性格和牺牲的观念。
人们很可能认为军队奖章是一个特殊事例,它追溯到有关荣誉和德性的古代伦理。而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分配经济繁荣的成果和困难时期的重负,以及如何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些领域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有关经济安排的对与错的争论,经常会将我们带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在道德上应得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讨论。
公众对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恰当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由抵押贷款所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现在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下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上的公司到了崩溃的边缘。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所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 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 [16]
2008年10月,乔治·W·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基金作为政府救助措施,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而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买单,这似乎很不公平。可是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它们草率的赌注(不完备的政府法规使之成为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这里的情形是:经济总体的福利似乎要超过对公平的考量。国会很不情愿地下拨了救助款项。
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 I. G)—一家保险业巨头,被旗下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投资而拖垮。尽管由于大量政府资金(总数达1 730亿美元)的注入获救,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了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是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 [17]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关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关于过高价格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关于用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地奖励那些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的成员。这一定有些不对头。尽管美国政府现在拥有该公司80%的股份,但是财政部长在请求由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取消奖金的发放时,却无功而返。首席执行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受控于美国财政部持续的、任意的管制,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他们拥有大半个公司—我们需要高水平的员工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 [18]
公众以盛怒予以回应。《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以头版头条表达出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浑蛋们,不要如此心急。” [19] 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政府救助款项的公司所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征收90%的税,以收回这笔钱。 [20] 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同意返回奖金,总计收回约5 000万美元。 [21] 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于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 [22] 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
对奖金事件的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公正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于政府救助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并相互冲突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人又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大灾难,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上来说,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观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们(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不配得到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配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正如报纸头条不留情面地指出的。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政府救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之。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者们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从而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都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他们仍然不觉得百万美元的奖金有什么不妥之处。 [23]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也(以更得体的方式)体现于国家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Sherrod Brown)(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性。 [24]
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和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 [25]
这种关于贪婪的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次经济崩溃后从救助款项中拿到的奖励,与经济繁荣时期从市场获得的奖励区分开来。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而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些政府救助奖金的领受者们要比多年前更加贪婪—而在那时候,他们非常成功并获得更高的奖金?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以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援助的钱来奖励贪婪是一种错,那么,难道市场对其的慷慨回馈就没有错吗?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发放奖金的一半。 [26] 如果我们现在说,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钱的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奖励贪婪,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前几年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于纳税人,而经济良好时期的奖金来自于公司的赢利。如果公众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得,那么奖金的出处就不应该影响这一判断。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于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这场民怨的核心: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奖励贪婪,而在于他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线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线却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成功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然而他明白,对失败的奖励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救助款项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当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当奖金来自于美国纳税人的钱。 [27]
有关政府救助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于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他是艾奥瓦州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于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们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么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 [28]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去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以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继续往外扔钱。” [29]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在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自己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 [30]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 [31] 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 [32]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助救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也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公正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灾难性的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的话,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以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们,又怎么能够由于那些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自身行为,而是他们不可掌控之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4倍的工资。 [33] 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仅仅是其工人的42倍。 [34] 难道1980年的那些首席执行官没有现在的这些有才华,也没有他们工作努力?抑或是,这些工资的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偶然情况与天赋和技能无关?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平均工资为1 330万美元(根据2004~2006年的数据),与之相对的是,欧洲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是660万美元,而日本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为150万美元。 [35] 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就应得2倍于欧洲同行、9倍于日本同行的工资吗?抑或是这些差距所反映出的因素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们付诸工作的努力和才能无关呢?
2009年年初,公众对于政府救助的愤怒纠结着美国,这表达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些通过冒险性投资而摧毁自己公司的人,不应当得到百万美元的奖励。然而,关于奖金的争论却引发了另一些问题—当经济良好时,谁应当得到什么。那些成功人士应得市场所赋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吗?这些丰厚收入是否取决于那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呢?在经济良好时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危机是否会促进公众去讨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时,便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当我们仔细考虑价格欺诈的对与错、关于紫心勋章的不同主张以及政府救助时,我们已经鉴别了三种分配物品的方式:福利、自由和德性。每一种理念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考量公正的方式。
我们当今的一些争论反映出我们在以下问题上的分歧:将幸福最大化、尊重自由以及培养德性意味着什么?而其他一些争论则涉及这样的分歧:当这些理念相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哲学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它却能够清晰地概括我们目前的这些争论,并澄清那些当我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时可能面对的各种观念背后的道德考量。
本书探索了这三种思考公正的方式各自的优缺点。我们将从福利最大化这一理念开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市场社会而言,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起点。许多当代政治争论都是关于如何促进经济繁荣,或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些事情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我们认为经济繁荣能够使我们过得更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换言之,经济繁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益于我们的幸福。为了探究这一理念,我们将转而讨论功利主义,它对我们应当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如功利主义者所说的)如何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为何如此这些问题作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
接着,我们将讨论一系列将公正与自由相联系的各种理论。这类理论大多数都强调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尽管它们自身在哪些权利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上存有分歧。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公正意味着尊重自由和个体权利这一观念与功利主义使幸福最大化的观念,至少同样为人们所熟知。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设定了某些大多数人都不能侵犯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环顾世界,公正意味着尊重某些普遍人权的观念,被越来越多地接纳(如果不总是实践上的,那么至少也是理论上的)。
从自由地角度考量公正是一种宽泛的理论。实际上,目前某些最激烈的政治争论就产生于这种理论内部的两大阵营—追求放任主义的阵营和追求公平的阵营。坚守放任主义阵营的是一些拥护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公正就在于尊重和维护达成一致意见的成人的自愿选择。讲究公平的阵营包括一些持平等主义态度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既不正当也不自由。在他们看来,要想达到公正,需要政策来修正社会和经济的缺陷,并给予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
最后,我们将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公正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代政治领域,德性理论经常被看成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宗教右派。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然而,以下这种观念—公正社会认可某些德性以及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引发了许多政治运动和争论。除了塔利班分子,废奴主义者和马丁·路德·金也从道德和宗教理想中引申出了各自的公正理论。
在我们试图评价这些公正理论之前,有必要先询问哲学论证如何能够展开—尤其是在像道德和政治哲学这样争辩如此激烈的领域。它们经常开始于具体的情境。正如我们在有关价格欺诈、紫心勋章以及政府救助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道德和政治的观点体现于分歧之中。这些分歧通常产生于公共领域中的不同党派或不同主张的倡导者之中;而有些时候分歧存在于作为个体的我们的内心,存在于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时无所适从和自相矛盾的时候。
然而,我们怎么能从那些在具体情境所作的判断中,精确地推理出我们认为应当适用于各种情境的公正原则呢?简言之,道德推理以何种形式存在?
为了探讨道德推理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转向两种情境—一个是哲学家们讨论较多的假想的故事,另一个是让人感到极其痛苦的、关于道德困境的真实故事。
让我们首先来考虑下面这个哲学家设想的故事。 [36] 像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它讲述了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在其中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只专注于有限的几个哲学议题。
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电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疾驰而来。在前方,你看见五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是你不能,因为刹车失灵了。你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的话,他们将全部被撞死。(我们先假定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突然,你注意到右边有一条岔道,那条轨道上也有一个工人,不过只有一个。你意识到,你可以将有轨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这个工人,而挽救那五个工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大多数人会说:“拐!尽管撞死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悲剧,可撞死五个人将会更糟糕。”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这看起来确实是正当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与有轨电车有关的假设。这一次,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旁观者,站在桥上俯视着轨道。(这次旁边没有岔道)轨道的那一头开来了一辆电车,而在轨道的这一头则有五个工人。刹车又一次失灵了,电车即将冲向那五个工人。你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避免这场灾难—可是突然你发现,你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你可以将他推下桥,落入轨道,从而挡住疾驰而来的电车。他可能会被撞死,但是那五个工人却将获救。(你考虑过自己跳下轨道,可你意识到自己太小了,无法挡住电车。)
将那个魁梧大汉推落到轨道上是否为正当之举呢?大多数人会说:“当然不是!将那个人推向轨道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将某个人推下桥致死看起来确实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即使这样做挽救了五个无辜的生命。然而这便产生了一个道德难题:为什么这一原则—牺牲一个生命以挽救五个生命—在第一种情况下看起来是正确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看起来是错误的呢?
如果像我们对第一种情形的反应所暗示出的:数目很重要—如果挽救五个生命比挽救一个生命更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第二种情形,去推那个人呢?即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将一个人推向死亡看起来也非常残忍。然而,用一辆有轨电车撞死一个人就不那么残忍吗?
将桥上的那个人推下去之所以不对,可能是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的意愿而利用了他。毕竟他并没有选择参与其中,他只是站在那里。
然而,我们可以对那个在岔道上工作的人说同样的话。他也没有选择要参与其中,他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这失控电车事件中,他并不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可能会辩解说,铁路工人甘愿冒这样的危险,而旁观者则未必会如此。然而,让我们在这里假设,在紧急情况下牺牲自己以挽救他人的生命并不在这份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这个工人与桥上的那个旁观者一样,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许这里的道德差别并不在于对受害者的影响—他们都会死亡,而在于作决定的那个人的意图。作为电车司机,你可能会这样为自己将电车拐向岔道而辩解:尽管你可以预见到在岔道上那个工人的死亡,但是你并没有想要他死。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那五个工人可以幸免于难,而这第六个人也能存活,这样,你的目的仍然能够达到。
然而,这一点在推人坠桥这一情形中仍然成立。你从桥上推下去的那个人的死亡,对你的目的而言并非不可或缺。他所要做的就是挡住电车,如果他能够既挡住电车而又存活下来的话,你将会非常高兴。
深入思考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两种情形应当依据同一原则来裁定。它们都涉及要故意选择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以防止一个更严重的损失。你可能仅仅是因为胆小脆弱—一种你应当克服的犹豫—而不情愿将那个人推落桥下。用自己的双手将一个人推向死亡看起来确实比转动电车的方向盘更加残忍,然而,做正当的事情并不总是轻而易举。
我们可以对这个假设稍作改变,以检验一下这一观念。假设作为旁观者的你,可以不伸手推就能使身旁的大个子掉进轨道;假设他正站在一个活板门上,你可以通过一个方向盘而打开这个活板门。不伸手推,便有同样的结果。这是否使得这成为正当之举呢?或者,这是否仍然比作为有轨电车司机的你拐向岔道在道德上更为恶劣呢?
要解释这些情形的道德差别并非易事—为什么使电车拐向岔道似乎是对的,而将人从桥上推下就是错的呢?不过,请注意我们在推理出两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区别时所遇到的压力—如果我们推理不出来,那么就要重新考虑我们在每一种情形中对何谓正当之举做出的判断。我们有时候将道德推理看做是说服他人的一种途径,然而,它同时也是一种澄清我们自身的道德信念,了解自己相信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途径。
某些道德困境源于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例如,一种在失控电车故事中起作用的原则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而另一种原则则认为,即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也是不对的。当我们面对一种情形—其中我们要挽救一些人的生命就必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便遇到了道德困境。我们必须弄明白哪一种原则更有说服力,或者更适用于这种情形。
另一些道德困境则源于我们不确定事情将如何展开。像失控电车这样的假设的故事,排除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它们假定我们确切地知道,如果我们不调转电车的方向盘,或不把那个大个子推下桥的话,有多少人会死去。这使得这类故事不能完美地指导现实行为,不过这也使得这些故事成为对道德分析有用的方法。通过悬置偶然性—例如,“如果那些工人看到了那辆失控电车并及时地跳开了呢?”—那些假想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剥离出重要的道德原则,并检验它们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真实的道德困境,它在某些方面与那个假想的失控电车的故事有些类似,然而,事态将如何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之变得更加复杂:
2005年6月,一个由美国海军士官马库斯·勒特雷尔(Marcus Luttrell)和其他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所组成的特殊军事小组,在阿富汗境内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进行一项秘密的前期侦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班领导人,他是奥萨姆·本·拉登的亲信之一。 [37] 据情报显示,这名领导人率领140~1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藏匿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庄内。
这一特殊军事小组在山脊上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俯瞰那个村庄。突然,两名阿富汗农民赶着上百只咩咩叫着的羊,和他们撞了个对面。他们还带着一个约14岁的小男孩。这些阿富汗人没有武器,美国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命令他们坐在地上,接着便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几个人。一方面,这些牧羊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另一方面,如果放他们走,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告诉塔利班分子,有一帮美国士兵在这里。
当4名士兵仔细考虑他们的可选择余地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带绳索。因此,捆住这几个阿富汗人以争取时机找到另一个藏身之处的办法,在此时并不可行。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要么杀了他们,要么放他们走。
勒特雷尔的一名战友认为要杀掉这些牧羊人:“我们是在敌后执行任务的现役军人,受高级长官的委派来到这里。我们有权做任何事情来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对军事行动有利是显而易见的;放走他们是不对的。” [38] 勒特雷尔难以抉择。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从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战友说得对,我们不能放走他们。可是问题在于,我还有另外一个灵魂,我的基督徒灵魂。它一直向我施压,有个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不停地告诉我:杀害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不对的。” [39] 勒特雷尔没有说清楚他所说的基督徒灵魂是什么意思,总之在最后,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杀害这些牧羊人。他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放走了他们。(他3个战友中有一个弃权了。)正是这一票,让他后来无比悔恨。
在他们释放那几个牧羊人一个半小时以后,这4名士兵发现自己被80~100名手持AK-47和火箭筒的塔利班分子所包围。在接下来的那场惨烈的战斗中,勒特雷尔的3名战友都遇难了,塔利班分子还击落了一架试图解救该海豹突击队的直升机,机上16名士兵全部遇难。
勒特雷尔身受重伤,他跳下山坡并爬行了3英里,来到一个普什图人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保护着他,不让他落入塔利班分子之手,直到他获救。
在回忆录中,勒特雷尔谴责自己所投的反对杀那些牧羊人的一票。他在一本有关此次经历的书中写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所做出的最愚蠢、最糊涂、最笨的决定。我当时一定是脑子出问题了。我投了这样一票,而我实际上知道这是签下我们的死亡执行令……至少,当我回顾这些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决定性的那一票是我投的,它会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栖息在东得克萨斯的一座坟墓里。” [40]
使这些士兵所处的困境如此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种不确定性,即他们不确定如果他们释放那些阿富汗人后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仅仅走开而已吗?他们会不会通知塔利班分子呢?然而,假如勒特雷尔当时知道,放走那些牧羊人会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斗,造成惨重损失—19名战友丧生、自己身负重伤以及军事行动的失败,他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对于勒特雷尔来说,当他回顾此事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会杀了那些牧羊人。考虑到接下来的灾难,人们对此难以表示反对。从数目的角度来看,勒特雷尔的选择类似于脱轨电车的情形。杀害这3名阿富汗人,将会挽救他的3个战友和那些试图解救他们的16名士兵的生命。然而,是哪一个版本的脱轨电车情形与此类似呢?杀害这些牧羊人像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呢,还是更像将那个大汉推落桥下?勒特雷尔预料到了危险,但仍然不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一事实说明,它跟推人坠桥的情形更为接近。
然而,杀害牧羊人的理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推人坠桥的理由更有说服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据结果怀疑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塔利班分子的同情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类比: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站在桥上的人使那辆电车的刹车失灵,以企图撞死那些在轨道上工作的工人(让我们假设他们是他的敌人),那么,将他推向轨道的道德理由会变得更加有力。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知道,他的这些敌人是什么人,以及他为什么想杀死他们。如果我们知道,轨道上的那些工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而桥上的那个大个子是个纳粹分子,他企图使刹车失灵而撞死他们,那么,将他推落桥下以挽救那些工人的理由,将在道德上更有说服力。
当然,很有可能那些阿富汗牧羊人并非塔利班分子的同情者,而是这场冲突的中立者,甚至是塔利班分子的反对者,他们是受到塔利班分子的胁迫而透露了美国士兵的藏身之地的。假设勒特雷尔和他的同伴们确切地知道这些牧羊人对他们没有危害,但是会被塔利班分子折磨而供出他们的位置,他们仍可能会杀了这些牧羊人,以掩护他们的军事行动和保护自己的生命。只是,与他们知道这些牧羊人是支持塔利班分子的间谍相比,他们在做出杀害这些牧羊人的决定时,将会更加痛苦,在道德上也更站不住脚。
我们很少有人会面临像山上的士兵或脱轨电车目击者所遇到的那样重大的选择。然而,我们通过力图解决他们的困境,来说明道德论证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以及公共领域中的展开方式。
民主社会中的生活充斥着关于对与错、公正与不公正的争论。有些人拥护堕胎合法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堕胎是一种谋杀;有些人认为公平需要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赚来的钱拿走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支持大学录取中的反歧视行动 (3) ,以纠正以往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对那些按成绩应当能被录取的人而言,是一种不公平的矫枉过正的歧视;有些人反对严刑逼供恐怖主义嫌疑分子,认为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称的道德的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阻止恐怖主义袭击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经常是某个人在竞选中获胜或失败的原因,所谓的文化战争也是由此而起。考虑到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讨论道德问题所怀有的激情和热烈程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的道德信念已经通过教育或宗教信仰的灌输固定成形,非理性思考能改变。
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道德劝导就是无法进行的,并且那些被我们看做是关于公正和权利的公共争论,就不过是不同教条的相互攻击,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食物大战。
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我们的政治会接近于这一情形,然而它本不该如此。有些时候,一场争论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些相互对立的关于公正和不公正、平等和不平等、个人权利和共同利益的争论,进行独立的思考呢?本书将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当人们面对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时,道德反思是如何自然地产生的?首先,我们对一件应该做的事—比如,将电车拐向岔道—怀有自己的观点或信念。然后,我们会开始思考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理由,并找出它们所依据的原则:“牺牲一个人的生命而避免更多人死亡是更好的。”接着,当我们遇到一种能证明这种原则是不对的情形时,我们便迷惑了。“我以前认为,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总是正确的,而现在将那个人推落桥下(或杀害那些手无寸铁的牧羊人)似乎又是不对的。”我们感觉到源自于这种困惑的压力,并想要把它弄明白。这便是导向哲学的本能。
当遇到这种张力时,我们可能调整我们对何谓正当之为的判断,或重新考虑我们最开始拥护的那个原则。当遇到新的情形时,我们在自己的各种判断和原则之间左思右想,用一个来修正另一个。在这种从行动领域向理性王国之间来回思考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上的转变,就是道德反思。
这种观念将道德争论看成我们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判断和我们通过思考所信奉的原则之间的互动。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然而,尽管传统深远,它仍然受到以下的挑战:
如果道德反思就在于在我们的判断和所认同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合宜点,那么,这种反思又如何把我们带向公正和道德真理呢?即使我们终其一生都能成功地将我们的道德直觉和有原则的信念整合在一起,我们又能有多大的信心能说这种结果不过是一系列自圆其说的偏见呢?
答案在于,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同志或一个公民同胞。当我们与自己争论时,这个对话者可以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然而,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普通公民比作一群被囚禁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所见到的所有景象都是墙上的影子,是他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投影。在这里,只有哲学家能够从洞穴中走出,来到阳光之下,从而见到事物的真相。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把哲学家再次诱骗至他们所生活的黑暗之中,那么由于哲学家看到了太阳,因而只有他才适合统治那些穴居者。
柏拉图的意思是:要想抓住公正的含义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我们就必须超越偏见和日常生活的惯例。我认为他是对的,可并非完全正确。穴居者们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如果道德反思是一种对话—如果它需要在具体情境中的判断和影响这些判断的原则之间左右权衡的话—它就需要各种观点和信念作为基础和材料,而无论它们多么片面和原始。一种与墙上影子毫不相关的哲学,只能催生出一种贫瘠的乌托邦。
当道德反思转变成政治反思时,当它询问应当用什么样的法律来管理我们的集体生活时,它就需要参与到城市的骚动中,参与那些使公众心烦意乱的各种争论和事件。政府救助、价格欺诈、收入不平等、反歧视行动、服兵役以及同性婚姻的讨论,都是政治哲学探讨的内容。它们促使我们不仅在家庭和朋友面前,也在我们国家的那些高要求的公民面前,阐述并维护我们的道德观和政治信念。
更为苛刻的还是政治哲学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他们都以一些激进的、令人惊讶的方式来思考那些使公民生活富有生气的观念—公正与权利,义务与同意,荣誉与德性,道德与法律。亚里士多德、伊曼纽尔·康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约翰·罗尔斯都是这样的人物。但在本书中,他们的出场却并不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本书并非一本观念史,而是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旅程,其目的并非在于向人们展示在政治思想史中谁影响了谁,而在于促使读者将自己关于公正的观念付诸批判性的检验,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这些想法来自何处。
1884年夏,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远离陆地一千多英里。他们的船—“米尼奈特号”(Mignonette)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了,他们几个人逃到救生艇上,食物仅剩两罐腌制的芜菁甘蓝,而且没有淡水。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是船长,埃德温·斯蒂芬斯(Edwin Stephens)是大副,埃德蒙·布鲁克斯(Edmund Brooks)是船员—据报纸报道,“这些人全都具有高尚的品德”。 [41]
这组船员中的第四个成员是船舱男仆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年仅17岁。他是个孤儿,这是他的第一次海上长途航行。他没有听取朋友们的建议,而是“怀揣年轻人的梦想”,认为这次旅途会使他成为一个男人。可悲的是,结果并不是这样。
四名被困的船员在救生艇上凝望着地平线,希望能有一艘船经过并解救他们。在最初的三天里,他们按定量分食了部分甘蓝。第四天,他们抓住一只海龟,并以这只海龟和剩下来的甘蓝维持了一些日子。然后,连续八天,他们什么都没吃。
当时,男仆帕克蜷缩在救生艇的小角落里。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喝了海水,并因此生了病,看起来快要死了。在他们经受严峻考验的第19天,船长达德利建议用抓阄来决定让谁死,这样其他人也许能够活下去。但是布鲁克斯拒绝了,因此他们没有抓阄。
接下来的这一天,仍然不见别的船只。达德利让布鲁克斯把目光移开,并向斯蒂芬斯示意,他们不得不杀掉帕克。达德利做了个祷告,告诉男孩他的大限到了,然后用一把袖珍小刀刺进他的喉部静脉,杀死了他。布鲁克斯摆脱了来自良心的谴责,分享了这可怕的施舍。三人以男仆的尸体和血为食,又支撑了四天。
救援终于来了!达德利用犹豫而委婉的口吻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获救过程:“第24天,正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一艘船只终于出现了,这三个人被救了上来。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他们被捕并接受了审判。布鲁克斯成为污点证人,达德利和斯蒂芬斯则被送上了法庭。他们直白地承认他们杀害并吃掉了帕克,他们声称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必要。
假如你是法官,你会如何裁决呢?为了使事情简化,我们先把法律问题放在一边,先考虑如果由你来决定杀死船舱男仆在道德上是否可以容忍,你将如何处理。
对此最强有力的辩护是:考虑到当时那种可怕的情境,他们有必要杀死一个人以挽救其他三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杀死一个人并吃掉他的话,四个人可能都已经死了。帕克又弱又病,是当时符合逻辑的候选人,因为他反正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他跟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不一样,他没有家属,他的死不会剥夺任何人的依靠,也不会留下悲痛的遗孀和子女。
这种论证至少会受到两种反驳:第一,人们会质疑,杀死男仆所获得的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是否真的大于它所带来的损失。即使我们考虑到所挽救的生命的数量、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幸福,允许这种杀害也可能会对社会整体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这会削弱反对谋杀这一规范的权威性,或增加人们将法律为己所用的可能性,抑或会使船长们更难招募到船舱男仆。
第二,即使将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在内,杀死男仆确实利大于弊,难道我们就不会痛苦地感觉到,杀害并吃掉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男仆是不对的吗?而这之所以不对的原因要超越于社会的得失算计之上?难道以这种方式利用一个人—利用他的脆弱,未经本人同意就剥夺了他的生命—是对的吗,即使这样做使他人受益?
对于任何一个对达德利和斯蒂芬斯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而言,第一种反驳似乎只是一种温和的抱怨。它接受了功利主义的这一假设—道德就在于权衡得失,道德仅仅期望一种更完备的、对社会后果的估算。
如果杀害这个船舱男仆值得引起人们道德上的愤怒,那么第二种反驳则更接近要点。它反驳这样一种观念:正当的行为仅仅是对结果—代价和受益—的一种算计。它暗示道德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某种与人类恰当地对待他人的方式相关的东西。
这两种思考救生艇案例的方式可以阐明两种不同的思考公正的角度。从第一种角度来看,一种行为之道德与否仅仅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后果;正当的行为,就是人们经过综合考虑后所做出的任何能够使事情达到最佳状态的行为。而从第二种角度来看,在道德方面,结果并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全部。某些义务和权利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而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依赖于社会性的后果。
为了解决救生艇一案,以及许多我们通常遇到的、没有这么极端的困境,我们需要探索一些更重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问题:道德就是计算生命、权衡得失呢,还是某些道德责任和人权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它们超越于这样的算计之上?如果某些权利在这方面是根本性的—假如它们是自然的、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和无条件的—我们该如何甄别它们呢?又是什么使得它们具有这样的根本性呢?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多次嘲笑自然人权观念,称它们为“踩在高跷上的废话”。他开创的哲学思想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它至今对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商业经理以及普通公民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边沁是英国道德哲学家和法律改革者,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其主要观点很简单,并对人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对边沁而言,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边沁通过下列推理得出了这一原则:我们都被痛苦和快乐的感觉控制着。它们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主宰着我们,并决定着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对与错的标准“与它们的王权紧密相连”。 [42]
我们都喜欢快乐而厌恶痛苦。功利主义哲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使得它成为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使功利最大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则,同时也是立法者的原则。一个政府在决定要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和政策时,它应当要做任何能够使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幸福最大化的事情。那么,什么是共同体呢?边沁认为,它是一个“想象的集体”,由组成它的个体总数所构成。因此,公民和立法者都应当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这项政策的所有收益相加,再减去所有的代价,它会比其他政策产生更多的幸福吗?
边沁在为“我们应当使功利最大化”这一原则进行论证时,做出了大胆的断言: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以反驳之。他主张,任何道德论证都必须含蓄地利用使幸福最大化这一理念。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相信某些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或权利;可是,除非他们相信,尊重这些义务和权利将使人类的幸福最大化—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否则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维护这些义务和责任。
边沁写道:“当一个人想要反抗功利原则时,他所引用的理由正来自于这个原则本身—而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所有的道德争论,如果被恰当地理解的话,都是关于如何应用这个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原则的争论,而并非关于原则本身的争论。“一个人是否可能移动地球呢?”边沁问道,“能,可是他必须先找到另一个地球以立足。”对边沁而言,这唯一的地球、唯一的前提、道德争论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功利原则。 [43]
边沁认为他的功利原则提供了一种道德科学,它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他提出了很多计划来使刑罚政策更有效、更人性化。其中一个就是环形监狱。在该监狱的中间有一个监视塔,这使得看管者可以监视囚犯,而囚犯却看不见他。边沁建议,可以将这个环形监狱交给一个私人的承包商(理想人选就是他自己)来运营,该承包商将管理监狱,以换取罪犯劳动所得的利润,这些囚犯将每天工作16个小时。尽管边沁的计划最终被否决了—它在当时过于超前了,可近些年在美国和英国,人们看到,将监狱承包给私人公司的观念却有所复兴。
边沁的另一项计划,就是通过为穷人建立一个自主筹款的救济院而改进“乞丐管理”。这一试图减少街头乞丐的计划,鲜活地阐明了功利主义的逻辑。首先,边沁论述道,在街上遇到乞丐会以两种方式降低行人的幸福感。对于心肠软弱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了一种同情之苦;而对于心肠较硬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一种厌恶之苦。不管哪一种方式,遇见乞丐都减少了普通大众的功利。因此,边沁建议要将乞丐从街上赶走,并将他们局限于救济院之内。 [44]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对乞丐而言不太公平,不过,边沁的确没有忽略他们的功利。他承认,某些乞丐会更乐于乞讨而不愿在救济院工作。但是他注意到,快乐而富足的乞丐远没有悲惨度日的乞丐多。他总结道,公众所忍受的痛苦的总量,要超过那些被赶到救济院的乞丐们所感受到的不幸福。 [45]
有些人可能担心,建造和运营救济院会给纳税人增加开支,减少他们的幸福并因此减少他们的功利。然而,边沁提出了一种方式,以使他的乞丐管理计划能够完全自主筹款:任何一个遇见乞丐的公民都有权将他带到最近的一个救济院。一旦被限制在救济院,每一个乞丐都不得不工作以支付他的生活费用,而这些费用都会记在一个“自我解放账户”当中。这个账户将包括食物、衣服、床铺的花销以及医疗费用和一份人寿保险—以防这个乞丐在偿清该账户之前就死掉了。为了激励公民不怕麻烦,愿意抓捕乞丐并将其送往救济院,边沁还提议,每抓住一个乞丐便奖励20先令—当然,这笔钱将加在该乞丐的账单上。 [46]
边沁还将功利主义的逻辑应用于同一社区内的房屋分配,以使居民从他们的邻居那里所受到的痛苦最小化:“在每个可能产生某种不良影响的群体附近,安置对这种不良影响有免疫力的群体。”例如,“在胡言乱语的疯子或者说话不检点的人附近,安置聋子和哑巴……在妓女和放荡的女人附近,安置一些年长的女人。”至于那些严重畸形的人,边沁建议将他们安置在瞎子们的居所附近。 [47]
尽管边沁的这一提议看起来似乎有些残酷,可是他的目标却并不苛刻。他仅仅想要通过解决减少社会功利的问题,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他的乞丐管理方案从来没有被采纳过,然而,它所表征出来的这种功利主义精神存活至今。在考虑当代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的事例之前,我们有必要质问,边沁的哲学是否可以反驳呢?如果是的话,理由是什么?
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由于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它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公民。虽然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个体也重要,但只有在每个人的偏好与他人的偏好统计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如此。然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自始至终坚持功利主义的逻辑,就有可能纵容许多无视人类基本尊严的行为,正如以下这些案例所表明的:
在古罗马时期有一种大众娱乐项目: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运用功利主义会如何看待这种娱乐:当狮子撕裂并吞食基督徒时,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然而,那些围在竞技场边欢呼着的观众们却感受到了狂喜。如果有足够多的罗马人从这一残暴的景象中得到足够多的快乐,那么,一个功利主义者又有什么理由来谴责它呢?
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担忧,这样的游戏会使人们变得粗野,因而在罗马的街头引起更多的暴力;抑或会引起那些潜在受害者们的恐惧和战栗,他们某一天也有可能被扔给狮子。如果这些后果足够坏的话,那么它们或许会超过这个游戏带来的快乐,并给功利主义者们禁止它的理由。但是,如果这种考虑就是反对为了娱乐大众而残害基督徒的唯一理由,那么,难道就没有丢失某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吗?
在当代争论中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在审问恐怖分子嫌疑人时,使用严刑逼供是否正当?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关于定时炸弹的情形:假设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你抓住了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你相信他肯定有一些关于一个核装置的情报,而这个核装置被设定于当天在曼哈顿爆炸。事实上,你有理由怀疑,就是他自己安装了这个炸弹。随着时钟滴滴答答地走动,他还是拒绝承认他是恐怖分子,或供出这个炸弹的位置。那么,我们能够正当地对他施行严刑拷打直至他供出炸弹在何处,以及如何解除它吗?
赞成这么做的理由源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尽管严刑逼供使嫌疑人遭受痛苦,极大地减少了他的幸福和功利;可是一旦炸弹爆炸,将会损失成千上万条无辜的生命。因此,你可能会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认为,如果使一个人遭受剧痛能阻止大范围的死亡和苦难,那么这样做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认为,对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嫌疑人使用残酷的审讯手段,帮助他们避免了另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他的这一论证就是基于功利主义的逻辑。
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者就肯定支持严刑逼供,某些功利主义者基于实际的理由而反对之。他们认为,严刑逼供很少起作用,因为逼迫之下所获取的情报经常不可靠。因此,我们是让他们受苦了,可是却并没有使共同体更加安全:集体的功利没有任何增加。或者,他们担心,如果我们的国家实施严刑逼供,那么,一旦我们的士兵被俘,他们将面临更加严酷的对待。如果综合起来考虑,这种与使用严刑逼供相联系的结果,可能在实际上减少了总体功利。
这些实际的考量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不管怎样,作为反对使用严刑逼供的理由,它们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它们并没有断言严刑逼迫一个人在本质上就是错的;而只是担心使用严刑逼供会有不良后果,而这不良后果从总体上来看会弊大于利。
有些人从原则上反对严刑逼供,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人权,也没有尊重人类的内在尊严。他们反对严刑逼供的理由并不依赖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认为人权和人类尊严拥有一个超越于功利的道德基础。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边沁的哲学就错了。
从表面上看,定时炸弹的情形似乎支持边沁的论证。数量似乎确实产生了道德上的差异。为了尊重一个无辜的船舱男仆的生命而接受救生艇上三个人可能死亡的事实是一回事;可是,如果像在定时炸弹的情形中,成千上万条无辜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呢?如果几十万条生命处境危险呢?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辩称,在某些时刻,即使是最热心的人权倡导者也会很难坚持认为让大量无辜的生命死去,比严刑拷打一个可能知道这个炸弹藏身之处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道德上会更加可取。
然而,作为对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一个考验,这个定时炸弹的例子具有误导性。它似乎证明了数目确实重要,因此,如果有足够多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话,我们应当放下对尊严和权利的道德顾虑。而且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道德终究还是在于算计得失。
然而,严刑逼供的情形并没有表明:挽救许多条生命的这样一种前景能够证明使一个无辜之人遭受严酷痛苦是正当的。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被严刑拷打以挽救那些生命的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事实上我们相信这个人安装了那枚炸弹。那么,那种支持我们严刑拷打他的理由的道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以某种方式对我们现在所力图避免的危险负有责任;或者如果他对这枚炸弹并没有任何责任,而我们认为他实施了其他可怕的行为使他应得残酷的对待。在定时炸弹这一案例中起作用的道德直觉并不仅仅是关于得失的算计,同时也是一种非功利主义的观念,即恐怖主义者是坏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我们将这个假设的情形稍作改动,排除任何假定的犯罪因素,那么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假如诱使该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开口的唯一方式,就是折磨他的年幼女儿(她对父亲穷凶极恶的行为毫不知情)。那么,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吗?我相信,即使是一个硬心肠的功利主义者也可能在这一想法面前退缩。然而,这个版本关于严刑逼供的情形,却给功利主义原则带来了一次更加真实的考验。它悬置了这样一种直觉—恐怖分子无论如何都应当受到惩罚(不考虑我们所期望获取的重要情报),同时,它也促使我们评价功利主义的计算本身。
第二种版本(涉及那个无辜的女儿)的关于严刑拷打的情形,使我们想起厄休拉·勒吉恩(Ursula K. Le Guin)的一个短篇小说:《离开欧麦拉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它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的故事。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为了不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过于理想而超出想象,作者告诉了我们有关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件事情:“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某栋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个房间,它有一扇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
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城市之美、他们的友谊之情以及孩子们的健康……甚至粮食的大丰收和风调雨顺的天气,都完全取决于这个孩子所受的可怕的痛苦……如果人们把这个孩子带出那个污秽之地以见天日,如果人们把他清理干净并喂饱他、让他感到舒适,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人们这样做,那么,欧麦拉人所有的繁荣、美丽和喜悦,在那一刻都将衰退并被毁灭。这就是条件。 [48]
这些条件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对边沁功利主义的第一种反驳主张维护基本人权,认为它们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即使它们能带来整个城市的幸福。侵犯那个无辜孩子的权利是不对的,哪怕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
功利主义声称能够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并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是其吸引力的一个主要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影响了很多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然而,为了使各种偏好能够相加,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这样一种通用价值货币。
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此表示怀疑。根据这种反驳,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价值都用同一种通用的价值货币来衡量。
为了探讨这种反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功利主义逻辑在得失分析中的应用方式—这种得失分析是一种被政府和公司普遍采用决策形式,它将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纳入货币术语之中,然后进行比较,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复杂的社会选择引入理性和精确性。
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在捷克生意做得很大—在捷克,吸烟仍然很普遍,并且得到社会认可。由于担心吸烟使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捷克政府近来在考虑提高烟草的税额。为了避免税额的增加,菲利浦·莫里斯成立调查团,针对吸烟对于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作了一个得失分析。该研究发现,吸烟给捷克政府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时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那么,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49]
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浦·莫里斯公关上的一场灾难。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他们却为此吹嘘。” [50] 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头上贴着一枚标价1 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浦·莫里斯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51]
有些人会说,菲利浦·莫里斯的吸烟报告说明了这种得失算计及其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上非常愚蠢。将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看做是有利可图的东西,这确实显示出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任何一项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关于吸烟的政策,都不仅要考虑对财政的影响,也要考虑公共健康和人类幸福的后果。
然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些深远后果的重要性—痛苦与磨难,悲恸的家庭以及生命的丧失。边沁发明了功利这一概念,用同一个尺度精确地表述我们关心的各种迥然不同的东西,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对于边沁学说的信奉者而言,吸烟报告并没有使功利原则陷入尴尬境地,它只是错误地应用了这些原则。一个更详尽的得失分析将会在道德计算中加入一个量,它代表了烟民的早死对自己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损失;这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还会将这些损失与烟民的早死给政府节省的开支作比较。
这就将我们带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价值都能被转换成货币术语?有些得失分析尝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去给人类生命定价。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下面两种对得失分析的运用,它们引发了道德上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人类生命的价值,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以功利主义的方式衡量了这一价值。
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平托(Pinto)是美国销售量最好的超小车型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当另一辆车从后面撞上它时,它的油箱容易爆炸。有500多人因为自己的平托汽车突然着火而丧生,有更多的人被严重烧伤。当其中一名烧伤受害者为这一设计缺陷状告福特汽车公司时,发现福特的工程师们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油箱的危险。然而,公司的经理们作了一项得失分析后认为,修补这种油箱所获得的利益(包括挽救的生命和减少的伤害)并不值得他们在每辆车上花费11美元—这是给每辆车装上一个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设置所需要的费用。
为了计算出更安全的油箱带来的益处,福特公司先假定如果不作改变的话,这种油箱会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然后,它给每一个丧失的生命和所遭受的伤害定价—一条生命20万美元,一种伤害6.7万美元。它将这些数目以及可能着火的平托的价值相加,得出这一安全性改进的总收益将是4 950万美元。而给1 250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11美元的装置将会花费1.375亿美元。因此,该公司最后得出结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远远高于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增加安全装置是不划算的。 [52]
得知这一研究,陪审团异常愤怒。它判给原告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和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该数目后来减至3 500万美元)。 [53] 可能陪审员认为公司给人类的生命定价是不对的,或者他们认为给一条命定价20万美元实在太低。但这一数目并不是福特公司自己定的,而是从一个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计算过一起交通死亡事故的花费。把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花费、葬礼的花费以及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赔偿加在一起,该机构将每例死亡的赔偿定为20万美元。
如果陪审团的反对只是针对这一价格而非原则,那么,功利主义者会对此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为了20万美元而死于一起交通事故,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活着。要衡量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对功利的全部影响,人们不得不考虑这个受害者未来幸福的丧失,而不仅仅是收入的损失和葬礼的花费。那么,什么才是对人类生命价格的更为真实的估算呢?
当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它也引起了道德愤怒,不过却是另外一种愤怒。2003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该机构给人类生命定了一个比福特公司更为慷慨的价格,可是却有一个根据年龄而调节的变量: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救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在这不同的价格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比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功利要少。(年轻人存活的时间更长,因此还能享受更多的幸福。)老年人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抗议这种“老年人的折扣”,并认为,政府不应当给年轻人的生命设定比年老人的生命更高的价格。由于受到这一抗议的冲击,环境保护署很快取消了这一折扣并撤回了该报告。 [54]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用这些情形来证明,得失分析具有误导性,并且给人类生命定价的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得失分析的拥护者们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选择都暗含着用一定数量的生命来交换其他物品和便利设施做法。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生命都有价格。
例如,汽车的普及必定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在美国,每年有超过4万人死于车祸。然而,这并没有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放弃汽车。实际上,它甚至都没有促使我们设定一个更低的限速。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国会下达了每小时55英里的全国限速。尽管此目的在于节约能源,可是,更低的限速效果之一就是减少交通死亡事故。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若干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限速提高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往返于家庭和工作;他们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并用这一收益除以增加的死亡数目。他们发现,为了贪图快速开车的方便,美国人实际上给每条生命定价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收益。 [55]
得失分析的倡导者们指出,通过每小时开65英里而不是55英里,我们含蓄地将人类生命价格定为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远远少于美国政府机构在设定污染标准和健康安全条例时通常使用的数字:每条生命600万美元。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明确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程度的安全来交换某些利益和便利,那么,我们应当睁大眼睛来进行此类交换,并应当尽可能系统地比较利益得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给人类生命标上价格标签。
功利主义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表现出的退缩倾向看做是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冲动,是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非理性禁忌。然而,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而言,我们的犹豫涉及一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亦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去解决这一争论。然而,某些信奉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却尝试过。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Edward Thorndike)试图证明功利主义的以下假设: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那些貌似迥然不同的欲望和厌恶,转化为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通用货币。他对一些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如果让他们遭受各种不同的经历,需要付他们多少钱。例如“如果让你拔掉一颗上门牙,需要付给你多少钱?”抑或“如果让你切掉一只脚的小脚趾呢?”抑或“如果让你生吞一条6英寸长的蚯蚓呢?”抑或“如果让你徒手掐死一只流浪猫呢?”抑或“如果让你在堪萨斯的一个远离于任何城镇10英里的农场度过余生呢?” [56]
你认为这些条目中的哪一项索价最高,哪一项索价最低呢?以下是他的研究所生成的价目表(按1937年的美元价值):
牙齿:4500美元
脚趾:57000美元
蚯蚓:100000美元
猫:10000美元
堪萨斯:300000美元
桑戴克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在同一尺度上加以衡量和比较。“任何需求或满足,都以一定量而存在,因此就是可度量的。”他写道,“一只狗、一只猫抑或一只小鸡的生命……主要是由它们的自然欲求、渴望、欲望以及满足所构成,并取决于这些……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尽管人类的自然欲求和欲望更多、更微妙、更复杂。” [57]
然而,桑戴克的价目表所具有的荒谬特征却表明了这种比较的荒诞性。我们真的能据此得出结论说:那些答题者认为在堪萨斯农场的生活前景的讨厌程度要3倍于生吞一条蚯蚓吗?还是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呢?桑戴克承认,有1/3的答题者声明,即使再多的钱也不能诱使他们遭受其中某些痛苦,这表明他们认为那些痛苦“令人厌恶到无法衡量的地步”。 [58]
也许我们没有压倒性的论据来支持或反对这样一种主张—所有的道德良善都能毫无损失地被纳入一种价值衡量。可是,这里还有一个案例使这一主张令人质疑:
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时,男生女生被分在不同的学院。女子学院不允许男性访客在女生宿舍过夜。这些规则很少能够得到执行,并且非常容易被打破,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大多数学院院长都不再将坚守传统的性道德观念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在持续的压力下,这一禁令是否应该放宽,成为圣·安妮女子学院争论的主题。
学院教员中有些年长的妇女是传统主义者,她们基于传统道德反对留宿男性访客。她们认为,未婚女青年与男子过夜是不道德的。可是,时代改变了,这些传统主义者们难以给出实际的理由以支持她们的观点。因此,她们将自己的论证转为功利主义的逻辑。他们认为,“如果男子留宿的话,学院的开支会因此增加。”会怎样增加呢?“他们要洗澡,因而会使用更多的热水。”她们还进一步论证道:“我们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单。”
改革者们通过以下这些妥协与那些传统主义者们达成了一致:每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有三个晚上留宿访客,而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的费用。第二天,《卫报》(Guardian)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逻辑转换成功利的逻辑并不容易。因此,不久之后,那些异性访问规定连同这个收费标准一起被撤销了。
我们已经考察了两种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反驳—一种认为它没有给予人类尊严和个体权利足够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它错误地将一切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都用单一的快乐与痛苦的尺度衡量。这些反驳在多大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呢?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作为比边沁晚一辈的哲学家,他试图改进功利主义,使之更加人性化,更少算计的色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之子,后者是边沁的朋友和追随者。詹姆斯·密尔在家里教育他的儿子,小密尔成为一个神童。他3岁学希腊语,8岁学拉丁语,13岁写成了罗马法律史,20岁精神崩溃—这使他消沉了几年。此后不久,他遇见了哈利特·泰勒。她当时已经结婚了,并有两个孩子,可她和密尔还是成为了亲密的朋友。20年后她丈夫去世,她跟密尔结婚了。密尔称赞泰勒是他在修改边沁学说的时候最有智慧的伴侣和合作者。
密尔的著作可以被看做是一次调和个人权利和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从边沁那里接受而来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艰难尝试。他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是英语世界为个体自由所作的经典辩护,其中心原则是:倘若不伤害到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政府不能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而干涉个体的自由,或将大多数人关于怎样最好地生活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密尔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负责的唯一一种行为,就是会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只要我不伤害到任何他人,那么,我的“权利的独立性就是绝对的。个体是他自己,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最高统治者”。 [59]
这种对个体权利的毫不让步的声明,似乎需要某些比功利原则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作为辩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假如一个大多数人的群体鄙视一个小的宗教,并希望它被禁止。禁止这个宗教难道不是有可能,甚至很可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吗?是的,被禁止的少数人会遭受不幸和挫败,可是,如果大多数人的数量足够多并且对此异端的仇恨之情也足够热烈,那么,他们的幸福之和将会远远超过那些少数人的痛苦。如果这一情形是可能的,那么功利原则似乎就不是宗教自由的稳固而可靠的基础。密尔的自由原则似乎需要一个比边沁的功利原则更为坚固的道德基础。
密尔对此并不同意。他坚持认为,个人自由的理由完全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考量之上:“我恰当地声明:我放弃任何可能从抽象权利观念得出的、独立于功利的、对我的论证有利的东西。我将功利看做是所有伦理问题的终极诉求,可是,这里所说的功利必须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功利,建立在作为进取性存在的人的永恒利益之上。” [60]
密尔认为我们不应当就事论事地使功利最大化,而应当从长远来看。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允许大多数人使持异议者保持沉默或抑制自由思考者,可能会使目前的功利最大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会使社会变得更坏—更加缺乏快乐。
为什么我们应当假设维护个人的自由和表达异议的权利会从长远上促进社会福利呢?密尔提出了几种理由:反对性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因而能给正统的观点提供纠正。即使它不正确,那么使正统的观点接受一些观念的有力挑战,将会防止它变成硬性的教条和偏见。最后,一个强迫其成员接受习俗和传统的社会很可能会陷入一种荒谬的一致性,从而剥夺了自身促进社会进步的能量和活力。
密尔对自由有益社会的效果所作的思考非常合理,可是它们并没有给个人权利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道德基础,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其一,如果为了促进社会进步而尊重个体权利,这会使权利具有偶然性。假设我们进入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通过专横的手段而达到一种长期的幸福,难道功利主义者不是就得承认,在这样一个社会,个人权利并非道德必需?其二,如果将权利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考量之上,那就遗漏了这样一种意义:侵犯某人的权利就是对这一个体施加了某种错误,而无论这给总体福利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大多数人迫害一种不受欢迎的信仰的追随者,无论这种不宽容从长期上来讲会给社会总体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难道这对作为个体的追随者们来说不是一种不公正吗?
密尔对这些质疑自有解答,但这也使他超越了功利主义伦理的边界。密尔解释道,强迫一个人根据习俗、传统或流行性的观点而生活是错误的,因为这妨碍他达到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对其人类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密尔看来,强制性顺从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敌人。
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做出选择时才得到运用。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最好的东西。心智和道德的力量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一个让世界或他自己周围的世界为他选择生活计划的人,除了类人猿的模仿能力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一个为自己选择计划的人,才能运用他所有的能力。 [61]
密尔承认,遵循传统可能会将一个人引入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并使他远离伤害。“可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相对价值是什么呢?”他追问道,“人们做什么事情固然重要,而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同样重要。” [62]
因此,行为和结果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品格也同样重要。对于密尔来说,个体价值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蕴含其中的幸福感,而是它折射出了人的品格。“一个人如果连欲望和冲动都不是自己的,他就没有品格可言,就像一个蒸汽机没有品格一样。” [63]
密尔对于个体性的有力赞颂是《论自由》一书的最显著的贡献。然而,它也是一种“异端邪说”。因为它诉诸一些超越于功利的道德理想—关于品格和人类繁荣的理想—它实际上并不是对边沁原则的一种阐释,而是对它的一种放弃,尽管密尔声称他的思想刚好与此相反。
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认为,功利主义将所有的价值都纳入一个衡量尺度,密尔对此的回应也同样依赖于那些独立于功利的道德理想。在《论自由》后不久,密尔又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功利主义》(1861),他在其中试图说明,功利主义者能够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
对于边沁而言,快乐就是快乐,痛苦就是痛苦。评判一种体验与其他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的唯一基础,就是它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和持久度。所谓的更高级的快乐或更高贵的德性只是能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快乐罢了。边沁并没有认识到不同的快乐所具有的质的差别。“快乐的量是平等的,”他写道,“图钉游戏与诗歌一样好。” [64] (图钉游戏是一种小孩子的游戏。)
边沁功利主义的部分吸引力正在于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它如其所是地接受人们的各种偏好,而不对它们的道德价值作任何评判。所有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边沁认为,认为某些快乐在本质上优于其他快乐,是一种专横的行为。有些人喜欢莫扎特,而有些人喜欢麦当娜;有些人喜欢芭蕾,而有些人喜欢保龄球;有些人读柏拉图,而有些人读《阁楼》 (4) 。边沁可能会质问道,有谁能说哪些快乐比其他的更高级、更有价值、更高尚呢?
这种拒绝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的行为,与边沁的以下观念紧密相连:所有的价值都能在一个尺度上加以衡量和比较。如果我们各种经验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量不同,我们就能在同一个尺度上衡量它们。然而,有些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对功利主义:他们相信,有些快乐是真的要比其他快乐“更高级”。他们认为,如果有些快乐是有价值的,而有些是卑劣的,那么,为什么社会应当平等地衡量所有的偏好呢?更不用说要将这些偏好的总和看做是最大善了。
让我们再来考虑罗马人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的情景。反对这一血腥景象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而一个更深入的反对的理由是:它迎合了那些邪恶的、而非高尚的快乐。难道改变这些偏好不比满足它们更好吗?
有人说,清教徒们之所以禁止犬熊相斗戏(古时的一种游戏),并不是因为它给熊所带来的痛苦,而是因为它给观众所带来的快乐。犬熊相斗戏已经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消遣,而斗狗和斗鸡却有一种持久的诱惑力,也有某些司法机关禁止它们。一种拥护这种禁令的理由是防止残忍地对待动物。但这种法律可能同样反映出一种道德判断—从斗狗中获得快乐是令人憎恨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阻止的事情,并非只有清教徒才同意这种判断。
边沁在决定法律应当如何判定的时候,会将所有的偏好都计算在内,而不考虑它们的价值。然而,如果更多的人宁愿观看斗狗而不愿看伦勃朗的油画,那么社会是否应当资助斗狗竞技场而不是艺术博物馆呢?如果某些快乐是卑劣可耻的,为什么我们在决定应当采用什么法律时要考虑它们呢?
密尔试图挽救功利主义免于这种非难。与边沁不同,他相信我们可以区分高级的和低级的快乐—评估我们欲望的质量,而不仅评估其数量和强度。他还认为除了功利本身之外,他可以不依赖于任何道德观念而做出这一区分。
密尔一开始就宣誓忠诚于功利主义的信条:“当行为能够促进幸福时,它们就是对的;当它们促进幸福的对立面时,它们就是错的。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快乐和摆脱痛苦,不幸福就是痛苦和缺乏快乐。”他也肯定了“这一道德理论所依赖的生活理论—即,源于痛苦的快乐和自由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所有值得追求的事物……都是因为其包含快乐,或者因为它能促进快乐,避免痛苦”。 [65]
尽管密尔坚持认为快乐和痛苦同样重要,但是他也承认“有些快乐比其他的更加值得欲求,更有价值”。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快乐在质量上更高一些呢?密尔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对于两种快乐而言,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都对其中某一种表现出明确的偏好,而不顾及任何道德责任感去偏爱它,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追求的快乐。” [66]
这个检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并没有远离功利主义的这一观念—道德完全并仅仅依赖于我们实际的欲望。密尔写道:“事物值得拥有的唯一标准就是人们想要他。” [67] 然而,作为一种能在不同的快乐之间做出质的区分的方式,他的检验似乎容易受到一种明显的反驳:难道没有这样一种情况—相比较于高级快乐,我们不是更喜欢低级的吗?我们不是经常更喜欢躺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而不去读柏拉图,或去剧院吗?难道我们不可能更喜欢这些要求不高的体验,而同时不认为它们特别有价值吗?
当我与学生们讨论密尔对更高级的快乐的描述时,我尝试了他的一种检验。我给他们展示了三种流行的娱乐项目:世界摔跤娱乐(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的一场比赛—场景闹哄哄的,其中那些所谓的摔跤手用折叠椅互相攻击;一场由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者所朗诵的《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以及《辛普森一家》的一个片断。然后我问了两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个节目,亦即哪个节目最令人愉快?你们认为哪一个节目是最高级的,或最值得的?
《辛普森一家》获得最多投票,被选为“最令人愉快的”,其次是莎士比亚。(一小部分勇敢者承认了他们对世界摔跤娱乐的喜爱。)然而,当被问及哪一种体验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质量时,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莎士比亚。
这一试验的结果向密尔的检验方法提出了质疑。许多学生更喜欢看霍默·辛普森,却仍然认为一段《哈姆雷特》的对白能带来更高级的快乐。不可否认,可能有些人之所以说莎士比亚更好,是因为他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并不希望自己被看成没有文化修养。也有些学生认为《辛普森一家》微妙地掺和了讽刺、幽默以及社会评论,它确实可以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相媲美。然而,如果大多数体验过这两者的人,都更喜欢看《辛普森一家》,那么,密尔可能就很难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具有更高的价值。
可密尔并不想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生活方式比其他的更加高贵,即使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更不容易感到满足。“相比较于一个较低级的人而言,一个拥有更高能力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来使他感到高兴,他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痛苦……然而,尽管具有这些不利因素,他却怎么也不会真的希望沦落成一种他感觉是更低级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一种要求我们运用更高能力的生活,去换取一种低级的、更容易感到满足的生活呢?密尔认为此处原因与“对独立和个人独立性的热爱”有关,他还总结道:“它的最恰当的称号就是一种尊严感,所有的人类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拥有这种尊严感。” [68]
密尔承认,“有时候在诱惑的影响下”,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会先选择低级快乐而推迟高级快乐。每个人偶尔都会抵挡不住成为电视迷的冲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伦勃朗和那些重复播放的节目之间的区别。密尔在一段令人难忘的话中表明了这一点:“做一个得不到满足的人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个满足的蠢货。如果一个蠢货或一头猪持有不同观点,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们只坚持自己的偏见。” [69]
这种对那诉诸更高人类能力的信念的表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密尔偏离了功利主义的前提。欲求事实上不再是判断何谓高尚何谓卑劣的唯一基础。现在,这个标准来源于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期望和欲求的、关于人类尊严的理想。更高级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它们而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更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作是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因为较之于低级的娱乐我们更喜欢它,而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
与我们关于个人权利所作的讨论一样,我们现在同样可以讨论更高级的快乐:密尔唯有通过援引一种脱离于功利本身的、有关人类尊严和人格的理想,才能使功利主义免于这样一种指控—它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一种关于快乐和痛苦的生硬的计算之中。
在这两位伟大的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中,密尔是一位更加人性的哲学家,而边沁则更为前后一致。边沁死于1832年,享年84岁。可是,如果你现在去伦敦的话,你仍可以看望他。他在遗嘱中写道,他的遗体要被保存、制成木乃伊并当作展品。因此,人们现在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他。在那里,他穿着他当时的衣服,忧郁地坐在一个玻璃容器之中。
在他死前不久,边沁扪心自问了一个与他的哲学相一致的问题:一个死去的人对于生者还有什么用呢?他总结道:一个用途就是将自己的尸体贡献于解剖学。然而,对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来说,最好还是保存他们的肉体以激励未来的思想家们。 [70] 边沁将自己置于第二类。
实际上,谦逊并不是边沁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他不仅为自己遗体的保存和展示提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提议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每年都要“为了纪念道德和立法领域中最大幸福的发现者”而聚会在一起。并且当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应当请边沁出席这一场合。 [71]
他的仰慕者们答应了。20世纪80年代,他自己命名的“自我肖像”(auto icon)出现在国际边沁协会的创立大会上。据报道,边沁会被推出来参加该学院的管理评议会,该会议记录将他记载为“出席,但没有投票”。 [72]
尽管边沁作了精心的准备,他的木乃伊的头部还是腐坏了。因此现在用一颗蜡制的头代替了他真正的头,为他自己守夜。他真正的头颅现在保存在地窖中,曾经一度被展示在一个盘子上,置于他的两脚之间。不过,学生们偷走了这个头颅,要求学校用一笔钱将其赎回,并将赎金捐给了一个慈善机构。 [73]
即使死了,杰里米·边沁仍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
每年秋天,《福布斯》杂志都会公布一份全美最富的400人榜单。连续十多年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都位居榜首;当他于2008年摘得桂冠时,《福布斯》估算他的净资产为570亿美元。跻身这个榜单的还有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排名第二,净资产500亿美元)、沃尔玛的拥有者、谷歌和亚马逊的创始人、各类石油大亨、对冲基金管理者、媒体大腕、房地产大亨、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名列第155位,净资产27亿美元)以及纽约扬基队的所有者乔治·史坦布瑞恩(名列最后一位,净资产13亿美元)。 [74]
美国经济上层的财富是如此巨大,即使是在一个经济较弱的州,成为一个亿万富翁都不足以进入《福布斯》400强。实际上,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整个国家1/3的财富,超过了底层90%的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之和。那些收入位于前10%的美国家庭,吸纳了41%的全部国民收入,并持有全部财富的71%。 [75]
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为严重。有些人认为这种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并支持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而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假如贫富差距并不是强迫或欺骗导致的,而是形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做出的选择,那么就并非不公平。
谁是正确的呢?如果你认为公正就意味着使幸福最大化,那么你可能会基于以下的理由而支持再分配:假设我们从比尔·盖茨那里拿走100万美元并分发给100名贫困的领受者,每个人领1万美元,那么,总体的幸福会增加。盖茨几乎不会想起这笔钱,而每一个领受者则会从这1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中获得巨大的幸福,他们集体功利的上涨会多于盖茨的功利的下降。
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能够被扩展至支持一种非常激进的、关于财富的再分配,它可能让我们把钱从富人那里转给穷人,直到我们从盖茨那里拿走的最后一美元对他所造成的伤害与跟它对接受者的帮助一样多。
这种罗宾汉式 (5) 的情形至少会遭到两种反驳—一种是来自功利主义内部的思考,另一种则来自功利主义的外部。第一种认为高税率,尤其是针对收入的高税率,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热情,从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如果经济大蛋糕缩水了,可再分配的财富就减少了,社会总体的功利水平也会下降。因此,在向比尔·盖茨和奥普拉·温弗里征过重的税之前,功利主义者可能得先询问一下这样做是否会导致他们的工作量降低,从而收入减少,最终减少再分配给穷人的那部分金钱的数量。
第二种反驳认为这些计算跑题了,它认为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侵犯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利。根据这一反驳,即使理由充分,未经盖茨和温弗里本人的同意而从他们那里拿钱,就是一种强迫。这侵犯了他们用自己的钱做任何他们喜欢之事的自由。那些基于这些理由而反对再分配的人经常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并不是以经济效率的名义—而是以人类自由的名义,支持不受约束的市场,并反对政府管制。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根本性的自由权—用自己拥有的事物去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只要我们同样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利。
如果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现代政府的许多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并侵犯了自由权。只有最小政府—一个只监督合同得到履行、保护私人财产不被偷盗、维持和平的政府—才能与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相容。任何一个做得更多的政府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
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三种类型的政策和法律,而这些政策和法律在现代国家中却是普遍存在的:
1. 反对家长式作风。 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反对那些保护人们不伤害自己的法律。有关系安全带的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有关戴摩托车头盔的法律。即使骑摩托车时不戴头盔是鲁莽的,即使头盔法能挽救生命并防止致命性的伤害,自由至上主义者们仍然认为这些法律侵犯了个体的决定承担何种风险的权利。只要没有第三方受到伤害,只要那些骑摩托车的人为自己的医疗账单负责,那么政府就没有权利来规定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可以冒什么样的风险。
2. 反对道德立法。 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反对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推进各种德性观念,或表达大多数人的道德信念。许多人认为卖淫不道德,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那些禁止自主的成年人从事这一行业的法律就是正当的。某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反对同性恋,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剥夺男女同性恋者们选择性伙伴的权利的法律就是正当的。
3. 反对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排除了任何要求一些人去帮助另一些人的法律,其中包括为了财富的再分配而征税。尽管富人通过资助较不幸者的医疗、住房或教育等而帮助他们是可取的,可这样的帮助应当由个人主动承担,而不是由政府来命令。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通过税收把财富再分配是一种压迫,甚至是偷盗。政府没有权利强迫富裕的纳税人为穷人买单,正如一个仁慈的小偷也没有权利从一个富人那里偷窃钱财分给流浪汉一样。
这种自由至上主义的哲学并没有应用在政治生活之中。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者们经常部分同意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在文化议题上的观点,如校园祈祷、堕胎以及是否应限制淫秽出版物等。许多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们在同性恋的权利、生育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等问题上,也持有类似自由至上主义者们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自由至上主义的各种观点突出地体现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支持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雄辩之中。但自由至上主义最早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这跟福利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恰好相反。在《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认为,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 [76]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认为许多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非法侵犯。社会保险或任何强制性的、国家运营的退休项目是他所列举的主要事例之一。他质问道:“如果一个人有意选择为今天而活,为了当下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资产,故意选择一种穷困潦倒的老年生活,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阻止他这么做呢?”我们可以呼吁这样的人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节省开支,“可是,我们是否有权利运用强迫手段阻止他去做那些他选择去做的事情呢?” [77]
弗里德曼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最低工资制度。政府没有权力阻止雇主给工人们支付他们乐意接受的任何工资—无论它有多低。政府在制定反雇佣歧视法时,也同样侵犯了个人权利。如果雇主希望基于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因素对他人区别对待的话,政府没有权力来阻止。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立法明显干涉了个体与他人自愿达成协议的自由”。 [77]
行业执照的要求也错误地干涉了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未经过培训的理发师想要给公众提供不太专业的服务,并且有顾客愿意冒险尝试一次价格低廉的理发,那么政府就无权禁止这一交易。弗里德曼将这一逻辑拓展至职业医师。如果我想做一次医疗费低廉的阑尾切割手术,我应当能够自由地雇用我选择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拥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确定他们的医生有能力,而市场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弗里德曼提议,与依赖于政府给医生颁发证书不同,病人可以将那些私人性的评级服务,如《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或《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作为一种认证标准。 [78]
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为自由至上主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哲学辩护,同时也向人们熟知的分配公正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从这样一种主张开始—个体拥有“如此强大和影响深远的权利”,以至于“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他总结道:“只有职责仅限于保证合同执行、保护人们不受压迫、偷盗和欺骗的最小政府,才是正当的。任何一个职责更加宽泛的政府都侵犯了个人不受强迫去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因此都是不正当的。” [79]
在那些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强迫去做的事情当中,最显著的一项就是帮助他人。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就强迫了富人,这侵犯了他们用自己的东西去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权利。
根据诺齐克的观点,那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没有任何错误。仅仅知道《福布斯》400强拥有几十亿美元而其他人身无分文,并不能使你得出任何关于这一安排是否公正的结论。诺齐克反对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一种公正的分配具有某种特定的模式,如平等的收入、平等的效用或基本必需品的平等供应。在他看来,核心问题在于分配是如何进行的。
诺齐克反对模式化的公正理论,而支持那些尊重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的公正理论。他认为分配公正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拥有的正当性和财产转移的正当性。 [80]
第一个条件关心的是你用来赚钱的资产是否一开始就是合法地属于你(如果你通过倒卖被盗的物品而赚钱的话,那么你就无权拥有这一收益)。第二个条件关心的是你是否通过在市场中自由交换,或接受他人对你的自愿馈赠而赚钱。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有权享有你拥有的那些东西,未经你的同意政府不得拿走它。只要没有人以不义之财起步,那么源于一个自由市场的任何分配都是正当的,无论它的结果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诺齐克也承认,判断经济领域各个行业的第一桶金是否干净并非易事。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几代人通过强夺、偷盗或欺骗而非法获得土地或其他资产呢?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现在那些跻身于上层的人是过去不正当行为—如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对美国原住民的征用—的受益者,那么根据诺齐克的观点,我们就有理由通过税收、赔偿或其他手段来纠正这种不公正。不过,我们要明白这些手段是为了矫正以往的错误,而不是为了产生进一步的平等。
诺齐克通过一个假想的篮球明星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的事例说明再分配的荒谬之处(正如他所认为的)。威尔特·张伯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工资达到了当时的最高额—每个赛季20万美元。由于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是当代偶像式的篮球明星,因此我们可以把诺齐克举的事例更换为乔丹。他在芝加哥公牛队最后一年的收入是3 100万美元—他一场比赛的收入比张伯伦一个赛季的收入还要多。
为了悬置任何有关初始获得的问题,诺齐克提议先假设你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你认为是公正的模式—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是一个完全平等的分配—来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初次分配。现在,篮球赛季开始了。那些想看乔丹打球的人每次买票的时候都在一个盒子里放五美元,最后盒子里的钱都归乔丹。(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乔丹的工资是由球队老板从本队的收入中支付的。诺齐克将这个过程简化为球迷直接付钱给乔丹,是为了集中讨论自由交换这一问题。)
由于很多人热切地想看乔丹打球,因此上座率很高,放钱的那个箱子变得很满。到赛季的末期,乔丹获得了3 100万美元,这远远多于其他人。结果,初始分配—你认为是公正的那种—再也不存在了。乔丹拥有更多,其他人拥有更少,而这种新的分配完全源于自愿的选择。谁有理由抱怨呢?不是那些出钱看乔丹打球的人,他们自由地选择了买票;也不是那些不喜欢篮球并待在家里的人,他们没有在乔丹身上花一分钱,与以前相比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当然更不是乔丹,他选择打篮球以换取一笔可观的收入。 [81]
诺齐克认为,这一情景说明了关于分配公正的模式化理论的两个问题:其一,自由推翻了模式。任何一个认为经济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人,都将不得不干涉自由市场,反复不断地制衡人们已经做出的选择的后果。其二,以这种方式干涉—向乔丹征税以资助那些帮助穷人的项目—不仅推翻了自由交易的结果,它还由于拿走乔丹的收入而侵犯了他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强迫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做出一份慈善贡献。
那么,向乔丹的收入征税到底错在何处呢?根据诺齐克的观点,道德上的风险要重于钱财。他认为,在这里受到威胁的正是人类的自由,其推理如下:“向劳动所得征税就等同于强迫人劳动。” [82] 如果政府有权索要我的一部分财产,那么它就也有权索要我的一部分时间。政府也可能会要求我花费30%的时间为它工作,而不从我这里拿走30%的收入。然而,如果政府能够强迫我为了它的利益而工作,那么它在本质上就对我拥有一种所有权。
获取某个人的劳动成果等同于从他那里获取时间,并命令他做各种行为。如果人们迫使你去做一段时间的某种工作,或做无偿的工作,那么他们就撇开了你的决定,而断定你将做什么事情,以及你的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使他们成为你的部分拥有者,这让他们对你拥有一种所有权。 [83]
这一推理路线将我们带到自由至上主义主张的道德核心—自我所有权的观念。如果我拥有自身,那么我就必须拥有我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有其他人能够命令我去工作,那么,那个人就是我的主人,我也就可能是个奴隶。)然而,如果我拥有我的劳动力,那么,我就必须有资格获得我的劳动成果。(如果他人有资格获得我的劳动成果,那么这个人就拥有我的劳动力并因此拥有我。)根据诺齐克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向迈克尔·乔丹的3 100万美元的收入征税以帮助穷人就侵犯了他的权利,因为这样其实就是断言,政府或共同体是他的部分拥有者。
自由至上主义者从征税(拿走我的财产)到被迫劳动(拿走我的劳动力)再到奴隶(否认我拥有自身)中,看到了一种道德上的关联:
|
自我所有权 |
拿走 |
|
人 |
奴隶 |
|
劳动力 |
被迫劳动 |
|
劳动成果 |
税收 |
当然,即使是最激进的个人所得税,也不会索要人们100%的收入,因此,政府并没有要求它完全拥有那些向其纳税的公民。可诺齐克坚持认为它确实要求拥有我们的一部分—只要政府为超过最小政府职责范围的事务向我们征税,我们对应于上缴的税款的那部分自主权就被剥夺了。
1993年,迈克尔·乔丹宣布退出篮球生涯,芝加哥公牛队的球迷失落万分。虽然他后来又复出了,并带领公牛队又夺得了三次冠军。但假设芝加哥市政厅或国会为了抚慰芝加哥公牛队球迷们的悲恸之情,通过投票要求乔丹继续打下一个赛季1/3的比赛的话,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样一个法律是不公正的,是对乔丹的自由的一种侵犯。可是,如果国会不能强迫乔丹重返篮球场(即使只是1/3的赛季),那它又有什么权力强迫乔丹放弃他靠打篮球所得的1/3的收入呢?
那些支持通过税收来重新分配收入的人们,对自由至上主义的逻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这些反驳大多数都能够得到解答。
如果你被征税,那么你总是可以选择少工作一点以交更少的税;可是如果你被强迫劳动,你就没有这样的选择。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回答 :是的。但是,为什么国家应当强迫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有的人喜欢观看日落,而有些人更喜欢那些需要花钱的活动—比如去电影院,出去吃饭,坐游艇航行,等等。为什么那些喜欢休闲的人,应当比那些更喜欢消费活动的人,交更少的税呢?
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类比:假如一个小偷闯进你家,他的时间只能允许他要么偷走价值1 000美元的平板电视,要么偷走藏在床垫下的1 000美元。你可能会希望他偷走电视,因为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再花1 000美元再买一台。可如果小偷盗走了现金,那么就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选择了(假设现在已经来不及退还电视以获取全额退款了)。但是,这种更希望损失电视(或少工作一些)的选择偏离了话题;那个小偷(或政府)在两种情况中都做错了,无论受害者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减轻他们的损失。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回答 :可能是这样。但这只是说服富人通过自由选择来援助穷人的一个理由。它并没有证明,强迫乔丹和盖茨捐助慈善是正当的。从富人那里偷钱给穷人,仍然是一种偷盗,而无论这是由罗宾汉来完成还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类比: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正在做透析的病人比我更需要我的一个肾(假设我有两个健康的肾),就意味着他有权得到它。国家也没有权利索要我的一个肾来帮助那名正在做透析的病人,而无论他的需要有多紧急、多迫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的。需求并不能践踏我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做想做之事的权利。
反驳3:迈克尔·乔丹并非单独作战,因此他欠那些对他的成功有所贡献的人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回答 :乔丹的成功确实依赖于他人,篮球赛是一种团队竞技。人们不可能支付3 100万美元来看他在一个空荡荡的篮球场上自由投篮。如果没有队友、领队、教练、裁判员、广播员以及场地维护人员等,他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收入。
可是,这些人的服务已经获得了其市场价值。尽管他们赚得比乔丹少,可是他们自愿地接受了对他们工作的回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乔丹一部分收入是他们的。即使乔丹亏欠他的队友和教练,我们也很难弄明白这种亏欠如何能够证明对他的财产征税以给饥饿者提供食品券、给流浪者提供公共住处是正当的。
反驳4:并不是真的没有经过乔丹本人的同意而对他征税。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制定他所遵从的法律时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回答 :民主的同意并不够。假设乔丹投票反对这项税务法,可是它最终还是通过了。美国国税局(IRS)会坚持让他交税吗?当然会。你可能会认为: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乔丹就表示同意(至少是含蓄地)遵守大多数人的意志并服从于法律。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仅仅由于作为公民而生活在此地,我们就给那大多数人写了一张空头支票,并事先同意遵守所有的法律,而无论它们正当与否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大多数就可以违背少数人的意愿而对其征税,甚至没收其财富和资产。那么,个人权利如何安置?如果民主的同意证明了拿走财产的正当性,那么它是否也证明了夺走自由的正当性?这个大多数群体是否可以剥夺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并声称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我已经对它的任何决定都表示同意了呢?
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对以上四种反驳都已经准备好了回答,可是还有一种反驳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们难以解决的:
反驳5:乔丹很幸运
他幸运地拥有那使他在篮球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能力,并幸运地生于这样一个社会,它奖励那种腾跃空中大灌篮的能力。无论乔丹如何努力地去发展他的技能,他都不能声称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些自然天赋,以及他有资格生活在一个喜欢篮球并愿意为之支付高报酬的时代。这些并不是他所作所为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在道德上有权利保留他的能力所带来的所有收入。共同体为了共同善而对他的收入征税,这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不义之事。
自由至上主义的回答 :这一反驳质疑乔丹的天赋是否真的是他的,可是这一论证路线可能非常危险。如果乔丹没有权利拥有那些源自于其能力的运用而获得的收益,那么他就并非真正地拥有这些能力;而如果他不拥有这些能力和技能的话,那么他也并不真正地拥有自身。可是,如果乔丹不拥有自身,那么谁拥有呢?你确定你想赋予政治共同体对其公民拥有所有权吗?
自我所有权这一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那些想为个人权利寻求一个牢固基础的人而言。我属于我自己,而非属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这一观念有力解释了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我的权利是不对的。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不情愿将那个大汉推落桥下以阻挡失控的电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他的生命是属于他的,才感到犹豫的吗?如果那个大汉自己选择跳下去以挽救铁轨上的工人,那么很少有人会反对。毕竟这是他的生命。可是他的生命并不能任由我们夺走或使用,即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也可以对那个不幸的船舱男仆说同样的话。假如帕克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挽救即将饿死的船员,那么大多数人会说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与他同船的船员们并没有权力自己夺走一条并不属于他们的生命。
许多反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人,会在其他领域援引自我所有权的观念。这可以说明自由至上主义观念具有持久的吸引力,甚至也吸引了那些赞成福利国家制度的人们。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自我所有权在一些论证—如关于生育自由、性道德以及隐私权的论证—中的体现方式。人们经常说政府不应当禁止避孕和堕胎,因为女性应当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也有些人认为法律不应当惩罚通奸、卖淫和同性恋,因为到达法定性成熟年龄的成人应当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性伙伴;有些人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拥有自己的身体,因此我应当自由地出售我的身体器官—而赞成为了移植出售自己的肾;有些人将这一原则拓展至维护辅助性自杀的权利—既然我拥有我自己的生命,那么只要我愿意,我就应当能够自由地结束它,并获得一位愿意帮助的内科医生(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我使用自己身体或处理自己生命的自由。
“我们拥有自身”这一观念体现在许多关于自由选择的论点之中。如果我拥有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和我自己本身,那么我就应当能够自由地用它们做任何我想做之事(只要我不伤害他人)。尽管这一观念很吸引人,可是要想欣然接受它的全部后果却并非易事。
如果你被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所吸引,并且想看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能走多远的话,就请考虑一下以下案例:
大多数国家都禁止买卖移植所用的器官。在美国,人们可以捐献他们的一个肾,却不能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可是有些人认为这些法律应当改变,因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肾移植中死亡—如果有一个买卖肾的自由市场,那么肾的供应量将会增加。他们还认为那些需要钱的人如果想卖的话,他们应当能够自由地出售自己的肾。
允许买卖肾器官的一个理由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观念:如果我拥有自己的身体,那么我应当能够自由地、如我所愿地出售我的身体器官。正如诺齐克所写:“‘对某物具有所有权’这一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决定对某物做什么的权利。” [84] 然而却很少有器官买卖的倡导者们接受这种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逻辑。
其原因在于大多数支持在市场上买卖肾器官的人都强调挽救生命的道德重要性,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捐出一个肾的人,都能够用另外一个肾继续生活。然而,如果你相信你的身体和生命是你的财产,那么这些考虑就都不真正重要。如果你拥有自身,那么你如自己所愿地使用自己身体的权利就是出售自己身体器官的一个足够的理由。你挽救的生命或你做的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
为了弄明白为何如此,让我们来想象两个有点极端的例子:
首先,假如那个想购买你另外一个肾的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他之所以出价8 000美元购买你(或更有可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的一个肾,并不是因为他十万火急地需要器官移植,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古怪的艺术品经销商。他向富裕的客户出售人体器官,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应当获许为了这种目的而买卖肾器官吗?如果你认为我们拥有自身的话,那么你就会很难说不。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如自己所愿地处理我们所有物的权利。当然,你也许会反对滥用身体器官,只赞成为了挽救生命而出售器官。然而,如果你持这种观点,那么你对器官自由买卖的辩护就不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你可能会承认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一种无限的所有权。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第二个例子。假如一个印度村庄里的某个艰难维生的农民,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他的孩子送进大学。为了筹这笔钱,他卖了一个肾给一个亟须进行移植的美国富人。若干年以后,当这个农民的第二个孩子也到了进大学的年纪时,另一个购买者来到了他们村庄,并出高价购买他的第二个肾。他还应当自由地出售这个肾吗?—即使这样会要他的命。如果器官买卖的道德理由基于自我所有权观念,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这个农民拥有自己的一个肾,而对另外一个肾就没有所有权—这说不通。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没有人应当被引诱为了钱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那么这个农民就有权出售自己的第二个肾,即使这样就等于出卖他的生命。(这一情形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囚犯想把自己的第二个肾捐给自己的女儿,但被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拒绝了。)
当然,我们可能仅仅允许那些用来挽救生命,并且不危害出售者生命的器官出售。然而,这样的一项政策就不是基于自我所有权的原则。如果我们真的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那就应当由我们来决定是否出售我们的身体器官,是否为了某种目的冒某种风险。
2007年,79岁的医生杰克·凯沃金(Jack Kevorkian)出现在密歇根的一个监狱,因为他八年来一直给那些身患绝症的、想死的病人提供致命性的药物。作为保释的条件,他同意不再帮助任何病人自杀。在20世纪90年代,凯沃金医生(他以“死亡医生”之名被人熟知)一直参加争取允许辅助性自杀的法律通过的运动,并且身体力行,帮助130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他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提供了一段长达60分钟的录像,这段录像记录了他实施谋杀行为的过程:他给一名患有路盖里格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的病人注射了一剂致命的药物。 [85] 在交出这段录像后不久,他被指控、审判,并被判为二级谋杀罪。
在凯沃金的故乡—密歇根州,以及在除了新奥尔良州和华盛顿州之外的其他任何一州,辅助性自杀都是违法的。许多国家禁止辅助性自杀,只有少数国家(最著名的是荷兰)明确地表示允许。
初看起来,支持辅助性自杀的论点似乎是自由至上主义哲学的一次书面申请。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禁止辅助性自杀的法律是不正当的,其原因如下:如果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那么我就应当可以自由地放弃它;如果我与某个人达成一个自愿的协议以帮助我结束生命,那么国家就没有权力干涉。
然而,允许辅助性自杀的理由,不一定要依赖于这样的观念—我们拥有自身,或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有些支持辅助性自杀的人并没有援引自我所有权,而是以尊严和同情的名义加以支持。他们认为,那些正遭受巨大痛苦的患有绝症的病人,应当能够加速他们的死亡,而不是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苟延残喘。甚至那些相信我们拥有维持人类生命的普遍义务的人们,都可能据此推论,在某些时刻,同情的要求超过我们维持人类生命的义务。
自由至上主义为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的辅助性自杀所作的推论很难脱离同情性的推论。为了评价自我所有权观念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让我们来考虑一个与绝症患者无关的辅助性自杀的案例。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怪异的案例,可是这种怪异却能让我们评价自由至上主义的逻辑本身,而不用考虑尊严和同情。
2001年,在德国罗滕堡的一个村庄,发生了一桩奇事。伯恩德–于根·布兰迪斯(Bernd-Jurgen Brandes),一名43岁的软件工程师,回应了一则网络上的广告。该广告寻找一些愿意被杀且被吃掉的人,由阿敏·迈维斯(Armin Meiwes)—一名42岁的电脑技术人员发布。迈维斯没有提供任何经济补偿,而只有这种体验本身。大约有200人回复了这则广告,其中四个人赶到迈维斯的农舍参加面试,但后来他们表示对此不感兴趣。然而,当布兰迪斯遇到迈维斯,并在喝咖啡时考虑后者的提议时,他同意了。后来,迈维斯杀死了他的客人,将尸体肢解,并把其装进塑料袋保存在冰箱里。直到他被捕时,这个“罗滕堡的食人者”已经吃掉了他那个自愿的受害者的40磅肉,其中一部分肉是他用橄榄油和大蒜烹饪过后再食用的。 [86]
当迈维斯被押受审时,这一骇人听闻的案件深深地震惊了公众,同时也让法庭非常困惑。德国没有禁止吃人的法律。辩护律师坚持认为,犯罪嫌疑人不能被判谋杀罪,因为这个受害人是自愿参与自己的死亡体验的。迈维斯的律师认为其当事人只是“被要求杀人”而有罪,这是一种辅助性自杀,最多只能判五年的有期徒刑。法庭将迈维斯判为过失杀人并判处八年半的有期徒刑,试图以此来解决这一难题。可是两年之后,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过于宽大的判决,并将迈维斯判为终身监禁。这一卑劣的故事以一种怪异的结局而收场。据报道,这名食人杀人犯在监狱中变成一名素食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工厂化农业经营太不人道了。
两个成人之间相互同意的同类相食,向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所有权原则以及由此得出的公正观念,提出了一种终极性的考验。这是辅助性自杀的一种极端的形式。由于它与缓解一名绝症患者的痛苦无关,因此它只能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我们能如自己所愿地对待它们—而得到辩护。如果自由至上主义的主张是对的,那么禁止达成同意的食人的法律就是不正当的,是对自由权利的一种侵犯。国家不能惩罚阿敏·迈维斯,就像它不能为了帮助穷人而向比尔·盖茨和迈克尔·乔丹征税一样。
许多我们现在争论得最热烈的、关于公正的话题,都与市场的作用有关: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吗?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或不应当用金钱购买的?如果有的话,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买卖它们又有什么错呢?
支持自由市场的理由一般基于两种主张:一种与自由有关,另一种则与福利有关。第一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让人们参与自由交换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干涉这种自由市场的法律,就侵犯了个人的自由。第二种是功利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自由市场促进了公共福利,当两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双方都获利。只要他们的交易使双方获益,而又不伤害任何其他人,那么它肯定会增加总体的功利。
市场自由的怀疑者们质疑这些主张。他们认为市场的选择并不总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自由,并且如果我们为了金钱而买卖某些东西和社会行为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被贬低。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这样一种道德—出钱雇用人们做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打仗和生孩子。通过这些有争论的事件思考市场的对与错,将会帮助我们辨清关于公正的主要理论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内战的最初几个月,集会的激情和爱国的情绪激发了北部几个州的好几万人自愿投身于联邦军队。可是在牛奔河战役中,联邦军队被打败;接着在第二年春天,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将军攻占里奇蒙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由此,北方人开始怀疑这场战争会不会很快结束。他们需要征召更多的士兵。于是,在1862年6月,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签署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份征兵法,而南方同盟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征兵法。
征兵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精神相冲突,于是联邦政府的征兵法对这一传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让步:任何被征召而又不想服兵役的人,可以雇用一个人来代替他。 [91]
于是,被征召入伍者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出1 500美元的高价寻求替代者,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南方同盟军的征兵法同样也允许雇用替代者,从而引发了这样一句口号—“富人的战争,穷人的战斗”,这种抱怨之声在北方也得到了回应。1863年3月,国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征兵法,试图平息这一抱怨。尽管它没有消除雇用替代者的权利,但是它规定:任何被征召入伍的人,可以向政府交纳300美元的费用而免除兵役。尽管这笔钱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一年的工资,但这项法律试图将豁免费控制在普通工人能支付的范围之内。有些城市和郡县向当地征召入伍者提供资助;一些保险公司每个月向受保人为某一险种征收一定的保险费,该险种将覆盖免除兵役的费用。 [92]
尽管这种代偿金旨在提供廉价的兵役豁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比允许雇用他人参军更加不受欢迎—也许因为这似乎是在给人类生命(或死亡的危险)定价,而且经过了政府批准。报纸头条宣称:“要300美元,还是要命?”对兵役法以及这300美元代偿金的愤怒引发了针对征兵军官的暴乱,最著名的是1863年6月纽约市的征兵暴乱,该暴乱持续了好几天,并夺去了一百多人的生命。第二年,国会制定了一项新的征兵法,取消了代偿金制度。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雇用替代者的权利在北方(尽管不在南方)却一直保留着。 [93]
最后,只有很少的应召入伍者在联邦军队中作战。(即使在征兵制确立之后,军队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由志愿兵组成,他们都是受大笔报酬或被征兵的威胁驱使而参军。)许多在征兵抽签中抽中号码的人都逃跑了,或由于残疾而被豁免了。在实际征召的大约27.7万人中,有8.7万人支付了代偿金,7.4万人雇用了替代者,只有4.6万人服了兵役。 [94] 那些雇用他人替自己打仗的人包括安德鲁·卡内基、摩根、西奥多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父辈,以及后来的总统切斯特·阿瑟和格罗弗·克利夫兰。 [95]
这种内战时的体制是一种正当的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吗?当我向学生们提出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说不。他们认为,允许富人雇用他人替自己打仗是不公平的。像许多在19世纪60年代参加示威游行的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这一体制是一种阶级歧视。
我接着问学生们,他们是支持征兵制,还是支持我们现在的志愿兵役制度。几乎所有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然而,这就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内战的体制不公平是因为让富人雇用他人为他们打仗的话,难道这一反对就不适用于志愿兵役制度吗?
当然,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安德鲁·卡内基不得不自己寻找替代者并直接付钱给他;现在,由部队招募士兵参加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战争,而我们—纳税人—集体地付钱给他们。然而,下列情形仍然存在:不愿意入伍的我们雇用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打仗。从道德上来讲,以上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内战中雇用替代者的体制是不公正的,那么志愿兵役制度不是也不公正吗?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让我们将内战体制放置一边,先考虑两种常规的征兵方式—强制征兵和市场征兵。
强制征兵扩充军队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要服兵役;或者,如果不需要所有人的话,就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将被召集。这一制度被美国人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越南战争时期,他们也使用了征兵制,尽管这一体制非常复杂,并且有大量的学生和占据特定职位的人们推迟参军,从而很多人避免了参战。
征兵制使人们更加强烈地反对越战,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提议废除征兵制;1973年,当美国军队逐渐从越南战场上退出时,志愿兵役制度代替了征兵制。由于兵役不再是强制性的,部队增加了报酬和其他福利,以吸引它所需要的士兵。
今天我们使用的“志愿兵役制”这一术语,指的就是通过运用劳动力市场—就像饭店、银行、零售商和其他生意一样—来扩充士兵队伍。“志愿兵役制”这一术语是某种误称。志愿兵并不像一支自愿的消防队—人们在这里服务却没有收入;也不像贫民施舍处—志愿者们在这里奉献自己的时间;志愿军是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士兵们在这里为了报酬而工作。这些士兵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才是“志愿者”:当获得报酬的雇员在任何职业中都是志愿者。没有人是被征召的,这份工作由那些自愿参军,以换取工资和其他利益的人履行。
关于一个民主社会应当如何扩充军队的争论在战争时期尤为激烈,如内战时期的征兵暴乱,以及越战时期的抗议所证实的那样。在美国采用了一种志愿兵役制之后,关于兵役分配的公正问题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关注范围。然而,由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又复兴了公众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民主社会通过市场的手段招募士兵是否正当呢?
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志愿兵役制,很少有人想回到征兵制。(2007年9月,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80%的美国人反对恢复征兵制,支持恢复征兵制的只占18%。 [96] )然而,这种再次兴起的关于志愿兵役制度和征兵制的争论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些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一些关于个人权利和公民责任的问题。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三种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征兵制、允许雇用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的制度)以及市场体制。哪一种是最为正当的呢?
1. 征兵制
2. 允许有偿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制度)
3. 市场体制(志愿兵役制度)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么答案就非常明显。征兵制(政策一)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具有强迫性,是一种奴役的形式。它暗示着政府拥有其公民,并且能够任意对待他们,包括强迫他们去打仗以及在战场上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罗恩·保罗(Ron Paul)是国会的一名共和党成员和自由至上主义的领军人物,近期他发表了如下主张以反对在伊拉克战争中恢复征兵制:“征兵制是一种奴役,这一点一目了然。第13次宪法修正案认定它是非法的,该修正案禁止非自愿的束缚。入伍者可能会丧命,这使得征兵制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奴役。” [97]
然而,即使你并不认为征兵制等同于奴役,你也可能基于这样的理由而反对它:它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并因此而减少了总体幸福。这是一种反对征兵制的功利主义的论点,它认为与一种允许雇用替代者的制度相比较,征兵制阻止双方受益的相互交换,从而减少了人们的福利。如果安德鲁·卡内基和他的替代者两人都想做一笔交易,我们为什么要阻止他们这么做呢?达成交换的自由似乎增加了每一方的功利,而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们来说,内战制度(政策二)要比纯粹的征兵制(政策一)更好。
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功利主义的观念会如何支持市场的推理。如果你认为一次自愿的交换使双方获益,而且不伤害其他任何人,那么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功利主义的理由任由市场来做出裁定。
如果我们现在比较内战制度(政策二)与志愿兵役制度(政策三)的话,我们也能明白这一点。为应征入伍者雇用替代者辩护的逻辑同样也可以为一种完全市场化的解决方式论证:如果你准备让人们雇用替代者,那为什么要先招募呢?为什么不简单地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招募士兵呢?—设定必要的工资和报酬来吸引所需士兵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让人们自己选择是否接受这个工作。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服兵役,那些想要服兵役的人们也可以独立判断总体上军事服务是否比其他选择更好。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志愿兵役制度似乎是三种选择中最好的一个。让人们根据所提供的报酬而自由地选择参军入伍,这就使得只有当服务于军事能够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那些不想服兵役的人也不必遭受以下这一功利的损失:即违背他们的意愿而被迫服兵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说志愿兵制度比征兵制度更贵。为了吸引所需要的士兵的数量和质量所支付的报酬和利益一定比士兵们被迫服兵役时要高。因此,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担心获得更高报酬的士兵们所增加的幸福会被为兵役支付更多的纳税人的不幸福感所抵消。
然而,这种反驳并不是很令人信服,尤其当备选项是征兵制(无论是否可以雇用替代者)的时候。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坚持以下这些观念是非常古怪的—即认为纳税人为政府的其他服务(如警卫和防火)所支付的各种花费应该降低,代价是强迫任意选出的人以低于市场价的报酬去执行这些任务;或者高速公路的维修费用应该降低,代价是要求一部分由抽签选出来的纳税人自己去做这份工作或雇用他人去做。由这种强制性的方式而产生的不幸福很可能会超过纳税人为支付更便宜的政府服务而获得的利益。
因此,从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推理方式来看,志愿兵役制度似乎是最好的,内战的那种混合制度位列第二,而征兵制是最不可取的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反驳来反对这种论证路线:一种反驳与公平和自由有关,而另一种则与公民德性和共同善有关。
第一种反驳认为,对于那些选择范围非常有限的人而言,自由市场并不总是自由的。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无家可归的、睡在桥墩下的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了睡在桥墩下,可是我们未必会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们也没有足够理由认为与睡在公寓里相比,他肯定更加喜欢睡在桥墩下。为了弄明白他的选择是反映出他喜欢睡在户外,还是反映出他支付不起一间公寓,我们就需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是自由选择这样做呢,还是迫不得已?
我们也可以对一般的市场选择—包括人们在承担各种工作时做出的选择,提出同样的质疑。这如何运用到军事服务的问题上呢?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主要社会背景,那么我们就不能判断志愿兵役制度是否公正:在这个社会中机会平等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是不是有些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或者对某些人来说,上大学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军入伍呢?
从市场推理的角度来看,志愿兵役制度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避免了征兵制的强迫性。它使得军事服务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可是,有些志愿服兵役的人可能与那些逃避兵役的人一样,其实并不愿意服兵役。如果贫困和经济困难的情况非常普遍,入伍的选择可能仅仅反映出选择余地的匮乏。
根据这一反驳,志愿兵可能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自愿。实际上,它可能涉及一种强迫的成分。如果社会中的一些人没有其他的好的选择,那么那些选择入伍的人实际上就是被经济需要强迫而参军。在这种情况中,征兵制和志愿兵役制度之间的区别,就不在于一个是强迫性的,而另一个是自由的;相反,每一种都采用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强迫—在第一种情形中是法律的强迫,在第二种情形中是经济需要的压力。只有当人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选择体面的工作时,我们才能说他们选择为了报酬而参军反映出了他们的偏好,而并非是选择余地的有限性。
如今我们志愿兵队伍的阶级构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反驳。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30 850~57 836美元)地区的年轻人不成比例地出现在现役部队的新兵队伍当中。 [98] 其中最少出现的是最穷的10%的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具备必需的教育和技能),以及最富的20%的人口(这些人来自于家庭收入在66 329美元以上的地方)。 [99] 近些年,超过25%的部队新兵都没有正式的高中毕业证书。 [100] 平民人口中46%的人接受过某种大学教育,但只有6.5%的18~24岁的现役军人曾经读过大学。 [101]
近些年,美国社会中最有特权的年轻人都没有选择服兵役。最近有一本关于武装力量的阶层构成的书,其标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擅离职守:美国上层社会在军事服务中未经允许的缺席》(AWOL: The Unexcused Absence of America’s Upper Classes from Military Service)。 [102] 普林斯顿大学1956届的750名毕业生中,有大多数人(450名)毕业后参军了;而在2006届的1 108名学生中,只有9个人入伍。 [103]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精英大学以及首都地区。只有2%的国会议员有子女在部队服役。 [104]
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是一名来自哈莱姆的民主党人,也是一位佩有朝鲜战争勋章的老兵。他认为这一情形是不公平的,并且号召要恢复征兵制。他写道:“只要美国人正在被送往战场,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作好准备,而不仅仅是那些由于经济条件窘迫而被划算的入伍奖金和教育奖励所吸引的人们。”他指出,在纽约市,“兵役负担的分配严重不成比例。2004年,这个城市70%的志愿兵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他们都是从低收入社区招募的。” [105]
兰格尔反对伊拉克战争,他相信如果政策制定者的孩子们不得不分担打仗的重任,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他还认为,考虑到美国社会中机会的不平等,通过市场来分配军事服务,对于那些只有最少选择余地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绝大多数为了这个国家在伊拉克服役的人都来自内陆城市内部或乡村地区的贫困社区;在这里,高达4万美元的入伍奖金和几千美元的教育津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有条件上大学的人而言,这些奖励与冒生命危险相比简直一文不值。 [106]
因此,对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的市场论点的第一种反驳,与不公平和强迫有关—阶级歧视的不公平,以及发生于以下情况的强迫:经济困难迫使年轻人甘冒生命危险来换取大学教育和其他奖励。
请注意,这并不是反对志愿兵役制本身,它仅仅适用于存在大量不平等的社会中运行的志愿兵役制。当这些不平等得到缓解时,你就能撤销这一反驳。例如,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会抱怨参军入伍的选择是出于经济需要被迫做出的,因而是不自由的。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强迫的危险总是存在于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的选择。我们需要多大程度的平等来保证市场的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社会背景条件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破坏了那些基于个人选择的社会制度(如志愿兵)的公平性?在什么条件下,自由市场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那些将自由—而非功利—作为公正核心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因此,让我们先搁置这些问题,直到后面几章我们讨论伊曼纽尔·康德和约翰·罗尔斯时再作讨论。
与此同时,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对运用市场来分配军事服务的反驳—以公民德性和共同善为名义的反驳。
这种观点认为军事服务不仅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公民责任。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相信,这种义务只能通过服兵役才能得到履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国家服务而得到履行,如参加和平队、美国志愿队、为美国而教的项目等。 (6) 可是,如果军事服务(或国家服务)是一种公民义务,那么将它放到市场上去出售就是不对的。
让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公民责任—出任陪审员的责任。履行陪审员的义务没有死亡风险,可是被召集出席做陪审员的任务却可能是非常繁重的,尤其是当它与工作或其他紧迫的任务相冲突的时候。可是,我们不允许人们雇用他人代替他们担任陪审员,我们也不允许运用劳动力市场来形成有报酬的、专业的“自愿者”陪审团制度。为什么呢?从市场论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支持这样做的理由。那个反对征兵制的功利主义的论点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征募陪审员:允许一个工作繁忙的人雇用他人替代自己,会让双方获益。最好废除强制征募陪审员的制度,让劳动力市场招募到足够的、合格的陪审员,就能使想要这份工作的人得到它,而让不喜欢这份工作的人避开它。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弃陪审员市场带来的社会利益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那些获得报酬的陪审员会过多来自贫困地区,担心司法的质量会受到影响。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富人比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更胜任陪审员的职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调整工资和津贴(就像军队所做的那样),以吸引那些具有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的人。
我们之所以招募,而不是雇用陪审员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在法庭上参与审判是一项所有公民都应当分担的责任。审判员并不只是投票,他们还与其他人就相关证据和法律进行商讨。而这种商讨吸收了陪审员们从多种多样的生活道路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履行陪审员义务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公民教育形式,是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体现。尽管陪审员义务并不总是能起到教化作用,但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它的这一观念,使法庭和人民之间保持着一种联系。
我们可以对军事服务说同样的话。支持征兵制的论点认为军事服务和陪审员义务一样,是一种公民责任,它体现并深化了民主公民身份。以这种观点来看,将军事服务变成一种商品—一种我们雇用他人来履行的任务—就腐蚀了那应当支配着它的公民理想。根据这种反驳,雇用士兵来为我们打仗之所以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对穷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放弃一项公民责任。
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M. Kennedy)就提出了这种论点。他认为:“美国现在的武装力量,具有很多雇佣军的特征。”他所说的雇佣军是指一支获得报酬的专业军队,这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它为之战斗的社会。 [107] 他并非有意贬低那些入伍士兵的动机,他所担忧的是,雇用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同胞来帮我们打仗,就让余下的我们都逃脱了,这就切断了民主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和那些以他们的名义而战的士兵们之间的联系。
肯尼迪评论道:“与人口成比例,如今在役的军事编制是当初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的4%。”这使得政策制定者们相对来说很容易将国家投入战争,而不需要获得社会整体的广泛而深入的许可。“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现在竟能够毫不费力地以一个社会的名义被送往战场。” [108] 志愿兵役制免除了大多数美国人为了国家而战斗、捐躯的责任。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因素,但这种从共同牺牲中的豁免却是以政治责任被腐蚀为代价的:
绝大部分无论如何都不会冒服兵役之危险的美国人,实际上雇用了一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同胞们,去做一些最危险的事情,而这些大多数则继续他们自己的事务,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心烦意乱。 [109]
最著名的、支持征兵制的公民理由,是由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一位出生于日内瓦的启蒙运动政治哲学家—提出来的。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务转变成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
当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主要事务,并且人们宁愿掏钱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时,那么,这个国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当必须奔赴战场时,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中……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公民们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不用钱来做任何事情。他们非但不付钱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花钱来购买那亲身履行自己义务的特权。我无法认同通常的观念,我相信强制劳役要比征税更不违反自由。 [110]
卢梭坚定的公民权观念及其对市场警惕的观点,看起来与我们现在的观念相差甚远。我们更容易将国家及其有约束力的法律和规则看做强制的范畴,而将市场及其自由交换看做是自由的范畴。卢梭会认为恰好相反—至少在涉及公民善的地方是这样。
市场的倡导者们可能会通过反对卢梭狂热的公民权观念,或否认它与军事服务之间的关联,而为志愿兵役制辩护。然而,卢梭激发的公民理想,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仍然能够引起一定程度上的共鸣。大多数志愿兵役制的支持者都强烈否认它等同于雇佣军。他们正确地指出很多人服兵役都是被爱国主义所激励,而不仅是受报酬和津贴所驱动。可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呢?如果这些士兵们表现非常好,我们又为什么应当关心他们的动机呢?即使我们把招募新兵的工作转移至市场,我们也会发现很难使军事服务脱离于古老的爱国主义和公民德性的观念。
因此,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代志愿兵和雇佣军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呢?它们都是付钱给士兵去战斗,都以工资和其他津贴的承诺来诱惑人们参军。如果市场是一种适当的招募军队的方式,那么,雇用士兵到底错在何处呢?
人们可能会回答道,雇佣军是外国国民,他们只是为了报酬而战,而美国志愿兵部队只雇用美国人。然而,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一种适当的招募士兵的方式,那么为什么美国军队在雇用士兵的时候要根据国籍而有所歧视?为什么它不应该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想要这份工作并且拥有相关的条件—中积极地招募士兵呢?为什么不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工资低廉而好工作又非常少—招募一支外国兵团呢?
人们有时候辩称外国士兵会不如美国人忠诚。可是国籍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忠诚,而且部队征兵者可以审查外国应聘者,以测定他们的忠诚程度。一旦你接受了“军队应当运用劳动力市场来扩军”的这一观念,那么,在原则上,你就没有理由将入选资格限定在美国公民之内,除非你相信军事服务毕竟是一种公民责任,是公民身份的体现。可是,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有理由质疑这种市场解决之道。
征兵制的结束距今已跨越了两代人了,美国人在将市场推理的完整逻辑运用于军事服务时仍犹豫不决。法国外籍军团则有着悠久的招募外国士兵为法国打仗的历史。尽管法国的法律禁止军团积极地在法国之外招募士兵,可网络却使这一限制变得毫无意义。它们以13种语言在网上征兵,现在已经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新兵。如今它们大约有1/4的兵力来自于拉丁美洲,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数比例也在逐渐上升。 [111]
美国没有成立外籍军团,不过它已经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延续,部队很难达到招募新兵的目标;面对这一困难,部队已经开始招募那些目前以临时签证居住在美国的外国移民,其诱惑包括高报酬和更快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现在大约有3万名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这一新项目将把入选资格从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拓展至临时移民、外国学生和难民。 [112]
招募外国士兵并不是市场逻辑演绎出来的唯一方式。一旦你将军事服务看做是一项工作,像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雇佣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完成。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将军事职责大规模地承包给私人企业。私人性质的军事承包商,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冲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构成了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7月,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在伊拉克,由美国人付钱雇用的个体工人的人数(18万人)超过了美国部队在那里的驻军人数(16万人)。 [113] 许多工人做的都是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建造基地、维修汽车、运输必需品以及提供饮食服务等。然而,也有大约5万人是携带武器的保安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保卫基地、军队和外交人员,经常遭遇战火。 [114] 超过1 200名个体工人在伊拉克被杀,但是,他们没有躺在盖着国旗的棺材中回归故里,他们的死亡数目也没有被包括在美国军队的死亡人数之内。 [115]
这些重要的私人军事公司之一就是黑水国际(Blackwater Worldwide)。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是前海豹突击队的成员,他热烈地信仰自由市场。他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他的士兵是“雇佣兵”,他认为这一术语具有“诽谤性”。 [116] 普林斯解释道:“我们在试着为国家安全机构做一些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曾经为邮政业所做的事情。” [117] 由于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所提供的服务,它在政府合同中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可是,它也经常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 [118] 它的角色最初于2004年获得公众的关注,当时,它的4名雇员在费卢杰遭到伏击并被杀害,其中两具尸体被挂在桥上。这一事件导致乔治·W·布什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攻入费卢杰,投入一场与叛乱分子的大规模、代价昂贵的战斗。
2007年,6名黑水公司的保安在巴格达广场上对人群开火,打死了17个平民。这些声称自己先遭到射击的保安躲过了伊拉克法律的起诉,因为这些法律是在美国入侵后由美国管理当局制定的。这些个体工人最终由于过失杀人而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起诉,并且这一事件导致了伊拉克政府要求黑水公司从本国撤出。 [119]
国会以及许多公众一般来说都反对将战争承包给像黑水国际这样的追求利益的公司。许多批评都集中于这些公司的不可信任问题,以及他们参与的虐待事件。在黑水射击事件发生的几年前,其他公司的雇佣工人一部分就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虐待被拘留者的人。尽管参与虐待的军队士兵受到了军法审判,可是那些雇佣工人却没有受到惩罚。 [120]
然而,假设国会对私人军事公司严加管理,以使得它们更加可靠,并使其雇员达到适用于美国士兵的行为标准,那么雇用私人公司来为我们打仗是否就无法反驳了呢?抑或,在付钱给联邦快递来传送邮件与雇用黑水公司来在战场上传送致命武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道德上的差别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解决一个先于此的问题:军事服务(或一般的国家服务)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的公民责任呢,还是一种被劳动力市场所恰当地管理的、像其他艰巨而冒险的职业(如采煤、商业捕鱼)一样的工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们相互之间负有什么样的义务,这些义务又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有关公正的理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一旦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几章中—明确了公民责任的基础和范围,我们就能更好地决定我们是应当招募士兵还是应当雇用他们。现在,让我们先来考虑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威廉(William)和伊丽莎白·斯特恩(Elizabeth Stern)住在新泽西州特纳夫莱镇,是一对夫妇。丈夫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妻子是一名儿科医生。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却无法生育,至少生育会对伊丽莎白带来生命危险—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因此,他们联系了一家安排“代孕”的不孕不育中心,该中心刊登广告以寻求“代孕母亲”—愿意为他人怀孕分娩,并以此获得报酬的妇女。 [121]
应征者中有一个妇女,名叫玛丽·贝丝·怀特海(Mary Beth Whitehead),29岁,有两个孩子,是一名环卫工人的妻子。1985年2月,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订了一份合同。玛丽同意用威廉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然后生下孩子,并在孩子出生后将他交给威廉;她还同意放弃她的母亲权利,这样伊丽莎白·斯特恩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就威廉这一方而言,他愿意支付玛丽1万美元(分娩时支付),外加医疗开支。(他还向该不孕不育中心支付了7 500美元,因为后者为他们安排了这次交易。)
经过多次人工授精,玛丽·贝丝怀孕了,并于1986年3月产下一名女婴。斯特恩夫妇盼望马上就能领养他们的女儿,给她起名为梅丽莎(Melissa)。然而,玛丽·贝丝·怀特海却改变了主意,她不想交出孩子,于是她带着孩子逃到了佛罗里达。但是斯特恩夫妇获得了法院命令,要求她交出孩子。佛罗里达警方找到玛丽,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斯特恩夫妇,而接下来关于监护权的争夺战也在新泽西法院展开。
初审法官不得不决定是否应该执行这份合同。你认为应当如何判决?为了使事情简化,让我们集中研究相关的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上,新泽西当时并没有允许或禁止代孕合同的法律。)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署了一份合同。从道德上来看,它是否应当得到执行呢?
赞成执行本合同的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是:交易就是交易。两个法定的成年人自愿达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协议:威廉·斯特恩将得到一个跟他有基因关联的孩子,玛丽·贝丝·怀特海将会因为9个月的工作而获得1万美元。
不可否认,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因此,你可能会基于以下两种理由中的一种,而犹豫是否要执行这份合同:首先,你可能会怀疑,当一个女人在同意为了钱而生一个孩子并在生下来之后放弃他的时候,她是否完整地得到了信息。她是否真的能预期到,当她要放弃这个孩子时,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不能,那么人们可能认为,她最初的同意被对金钱的需求所蒙蔽,也由于不够了解与孩子分开会怎样而被蒙蔽。其次,你可能会发现买卖孩子或租赁妇女的生育能力是不对的,即使双方都自由地同意这样做。人们可能会争辩道,这一行为将孩子变成了商品,并通过将怀孕和生孩子看成是赚钱的交易而剥削利用了妇女。
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婴儿M”这一案件的初审法官哈维·索尔考(Harvey R. Sorkow)并没有被这些反驳中的任何一个所说服。 [122] 他援引合同的不可侵犯性来维护这一协议。交易就是交易,这名生育母亲并不能仅仅因为她改变主意了就有权利解除合约。 [123]
该法官讨论了上述两种反驳:首先,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玛丽·贝丝的同意并不是自愿的,她的同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一方占据更高的交易地位。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每一方的服务价格都已经确定,因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没有一方强迫另一方,没有一方拥有专门知识因此而让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也没有一方拥有不相称的交易权力。 [124]
其次,他反驳了这样一种看法—代孕等同于出卖婴儿。该法官认为,威廉·斯特恩是孩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他并没有从玛丽·贝丝·怀特海那里购买婴儿。他只是因为她提供了怀孕和分娩孩子的这一服务,而给她支付了报酬。“出生后,这位父亲并没有购买这个孩子,她是与他自己的生物基因有关联的孩子。他不能购买已经属于他的东西。” [125] 由于这个孩子是由威廉的精子受孕而来,那么,她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孩子。因此,这里并没有涉及出售婴儿。那1万美元的报酬是为一项服务(怀孕)而非一个产品(这个孩子)支付的。
对于那种认为提供这样的服务剥削利用了妇女的观点,索尔考法官也提出了异议。他比较了有偿怀孕和有偿精子捐献。既然男人可以出售他们的精子,那么女人就应当能够出售她们的生育能力:“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提供生育的手段,那么,人们就必须同等地允许女人也能这样做。” [126] 他陈述道,与此相反的主张才是否定女人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玛丽·贝丝·怀特海将这一案件上诉至新泽西最高法院。该法庭全体一致推翻了索尔考法官的判决,并判这一代孕合同无效。 [127] 然而,它将梅丽莎的监护权判给了威廉·斯特恩,理由是:这对孩子来说最好。该法庭将合同搁置一旁,认为斯特恩夫妇会更好地养育梅丽莎;然而,它恢复了玛丽·贝丝·怀特海作为孩子母亲的身份,并要求低级法院给予她探视权。
在为法庭写结案陈词时,首席大法官罗伯特·威伦茨(Robert Wilentz)反驳了代孕合同。他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愿的合同,而且它包含了买卖婴儿的成分。
首先,这里的同意是有缺陷的。玛丽·贝丝在同意生养一个孩子并在出生后将孩子返还给他人时,并不真正自愿的,因为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
在这一合同中,那名自然意义上的母亲在了解她与孩子之间那种纽带的力量之前,给出了不可撤销的承诺。她从来都没有做出一个完全自愿的、基于完整信息的决定。因为很明显,任何在孩子出生之前所做出的决定,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信息不全面的。 [128]
一旦这个孩子出生了,这个母亲就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做出一个信息全面的决定。可是到那时,她的决定就不自由了,而是被“起诉的威胁,以及1万美元报酬的诱惑”所强迫,这使得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自愿的”。 [129] 此外,对金钱的需要,使得这个贫困的妇女很可能会“选择”去给富人当代孕母亲,而不是“被选择”。威伦茨法官提议说,这一点也对这类协议所具有的自愿特征提出了质疑:“我们怀疑,低收入阶层的不孕不育夫妇,是否会找高收入的人代孕。” [130]
因此,使得这份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里的同意是有问题的。然而,威伦茨法官还提出了第二种更具根本性的理由:
先将她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金钱需要的强迫,以及她对最终结果的理解有多深入这些问题搁置一边,我们认为她的同意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131]
威伦茨认为,商业性的代孕等同于出售婴儿,而出售婴儿是不对的,无论它是否自愿。他反驳了这一观点—这里的报酬是为了代孕母亲的服务,而并非是为了这个孩子。根据这份合同,只有当玛丽·贝丝交出监护权并终止其做母亲的权利时,才能向她支付这1万美元。
这就是在出售一个孩子,至少是在出卖一个母亲对其孩子所拥有的权利;这里唯一缓和的因素在于,购买者是孩子的父亲……一个中间人,受利益驱动而促成了这桩买卖。无论是什么样的理想推动了任何一方,利益的动机都支配、渗入并最终控制了这一交易。 [132]
那么,在“婴儿M”一案中到底谁是对的呢?—是执行该合同的初级法院,还是使该合同作废的高级法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评估合同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以及在反对代孕合同时所提出来的两种反驳。
那种支持代孕合同的论点所依据的是我们迄今所考察的两种公正理论—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反映了选择的自由。支持两个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所达成的合同,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功利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推进了总体福利。如果双方都认同一个交易,那么双方都肯定能从这一协议中获得一些利益或幸福,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笔交易。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这一交易减少了另外一些人的功利(而且要超过它给交易双方所带来的利益),否则,那些互相获利的交换—包括代孕合同—就应当得到支持。
这些反驳有道理吗?它们具有多少说服力呢?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关于什么算做过分的压力,什么算做缺乏信息的同意,人们还会有争论。可是,这种争论的要点在于判断出什么时候一个看上去像自愿的协议是真正自愿的,而什么时候并不是。这一问题清楚地体现于“婴儿M”一案中,正如它体现于关于志愿兵役制的争论中一样。
如果我们从这些案例中退后一步,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关于一个有意义的许诺的必要背景条件的争论,实际上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考察的三种公正进路中的其中一种公正理论—那种认为公正就意味着尊重自由—的家族内部的争论。正如我们所见,自由至上主义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它认为,公正需要尊重人们所做出的任何选择,假如这些选择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话。其他一些将公正看做是尊重自由的理论家们则在选择的条件上设定了一些限制。他们认为—正如法官威伦茨在“婴儿M”一案中所说的那样—迫于压力或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许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自愿。当我们开始讨论约翰·罗尔斯(一个自由阵营内部的成员,他反对自由至上主义关于公正的论述)的政治哲学时,我们将会更有能力来评价这一争论。
那么,对代孕合同的第二种反驳—认为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应当用金钱购买的,包括婴儿和妇女的生育能力的观点—又如何呢?买卖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错呢?对此,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将婴儿和怀孕看做商品就是贬低了它们,而没有适当地尊重它们。
潜藏在这种答案背后的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思想:正确地尊重商品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特定的尊重模式适用于特定的商品和行为。在商品的情形中,如汽车和烤面包机,最合适的尊重它们的方式就是使用它们,或制造、出售它们以获得利益。可是,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物都看做商品,那就错了。例如,将人类看做商品—看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人类是值得尊重的、而不是被使用的对象。尊重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的重视模式。
当代道德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便将这种论点运用于关于代孕的争论。她认为,代孕合同由于将孩子和妇女的劳动看做商品,因而贬低了他们。 [133] 这里她所说的“贬低”,意指“根据一种较低的,而非适合于它的评价模式来对待某物。我们不是‘更多’或‘更少’地来评价事物,而是以某种质上更高或更低的方式来对待事物。爱一个人或尊重一个人,就是以一种高于这个人被利用时所得到的对待方式,来对待他……商业化的代孕贬低了孩子,因为它将孩子们看做商品。” [134] 它将他们作为赚钱的工具加以利用,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值得爱护和关心的人加以珍惜。
安德森认为,商业化的代孕,通过将妇女的身体看做工厂,并付钱让她们与自己所生的孩子脱离关系,从而贬低了妇女。它用那些管理普通生产的各种经济规范,代替了那“通常管理孕育孩子的亲子规则”。安德森写道,通过要求代孕母亲“压抑她对这个孩子所感受到的母爱”,代孕合同“将妇女的劳动转换成一种异化了的劳动”。 [135]
在代孕合同中,(母亲)同意不与她的后代形成或试图形成一种母子关系。她的劳动是异化了的,因为她必须放弃其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怀孕这一社会行为所正当地推进的—一种与她的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 [136]
安德森的中心论点是:物品之间有所差别,因此以同样的方式—作为赚钱的工具或被利用的对象—来对待所有的物品是不对的。如果这一观点是对的,那么它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这一论点也对功利主义发起了挑战。如果公正仅仅是使快乐减去痛苦后的余额最大化,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方式,来衡量和评价所有的事物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或痛苦。边沁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了功利的概念。可是安德森认为根据功利来评价所有的事物,就贬低了那些更适合用更高的规范来加以评价的各种事物和社会行为—包括孩子、怀孕和对子女的养育。
可是,这些更高的规范是什么呢?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评价模式适合于哪些物品和社会行为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开始于自由的观念。由于人类拥有自由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当被仅仅当做对象而加以利用,相反,我们应当得到体面而尊重的对待。这种解决的路径强调(值得尊敬的)人与(仅供使用的)对象或物品之间的区别,是道德中最具根本性的区别。对这一路径的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他。
对更高规范的另一种路径,始于这样一种观念:正当的评价事物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取决于这些行为所满足的目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在反对代孕的时候,安德森论述道,“怀孕这一社会行为正当地促进了”一种特定的目的,即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一个要求这个母亲不要形成这样一种纽带的合同是贬低性的,因为这使她远离了这一目的。它以一种“商业生产的规范”代替了“亲子关系的规范”。这种思想—我们试图抓住这些行为的本质性目的或意图,以此来鉴别出那些适合于这些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考察他的论证过程。
我们只有考察了这些道德和公正理论,才能真正地裁决哪些物品和社会行为应当由市场来管制。然而,关于代孕的争论,如同关于志愿兵役制的争论一样,让我们瞥见了那危如累卵的一面。
曾经以“婴儿M”而广为人知的梅丽莎·斯特恩最近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了,专业为宗教学。 [137] 至今距离新泽西的那场著名的、关于她的监护权的争夺已经有二十余载,可是关于代孕母亲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商业性代孕;在美国,超过12个州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了,另有12个州禁止这一行为,而在其他一些州,其合法与否仍然不是很明确。 [138]
新的生育技术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代孕经济,并加深了它所体现出的伦理困境。当玛丽·贝丝·怀特海同意为了报酬而怀孕时,她提供了卵子和子宫,因此她是婴儿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然而,试管受精的出现使得由一位妇女提供卵子而另外一位来孕育它成为可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德博拉·斯帕(Deborah Spar)分析了这种新型代孕的商业优势。 [139] 从传统意义上说,那些签署代孕合同的人,“本质上要购买一个‘卵子加子宫’的包裹”,现在她们可以从一处获得卵子(多数情况下包括那个有意向的母亲),而从另一处获得子宫。 [140]
斯帕解释道,这种供应链条的断开,推动了代孕市场的发展。 [141] “通过断开卵子、子宫和母亲这条传统的连接,妊娠代理减少了那些围绕着传统代孕的、法律上和情感上的危险,并因此给一个新型市场的繁荣打开了空间。”“由于从卵子–子宫这一捆绑中解脱出来”,代孕代理人如今在选择代孕者时“更加具有歧视性”—“寻找带有特殊基因特征的卵子,以及依附于某种特定人格的子宫”。 [142] 那些可能要代孕的父母,不再需要担心他们所雇用来孕育他们的孩子的那个妇女的基因特征,“因为他们从别处获得这些”。 [143]
他们不在乎她长得怎么样,也不再那么担心她生出孩子后会索要孩子,或法庭将倾向于帮助她。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健康的妇女,愿意经受怀孕的辛苦以及在怀孕期间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 [144]
尽管妊娠代理增加了预期代孕者的供应量,需求量也同样有所增加。如今,代孕者们每次怀孕可以得到2万~2.5万美元的报酬。一次这样的安排(包括医疗费用和法律费用)一般来说总共要花费7.5万~8万美元。
由于价格飙升,人们不难发现那些预期要代孕的父母开始寻找便宜一些的替代者。像在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有偿怀孕现在开始被承包给廉价的供应方。2002年,印度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以期望能够吸引国外的顾客。 [145]
位于印度西部的城市亚兰德很快将成为有偿代孕中心,就像班加罗尔是呼叫中心一样。2008年,这个城市有超过50名的妇女为来自美国、中国台湾、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夫妇代为妊娠。 [146] 那里有一家诊所,给15个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当代孕母亲的孕妇提供集体住房,并配有仆人、厨师和医生。 [147] 这些妇女所挣的钱从4 500美元到7 500美元不等,通常超过她们15年所挣的钱,并使她们能够购买一栋房子或支付她们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 [148] 对于那些满怀希望奔赴亚兰德的夫妇而言,这一安排是笔好买卖,总开支大约2.5万美元(包括医疗支出、代孕者的报酬、往返机票、两次旅程的旅馆开销),大概是在美国代为妊娠总开销的1/3。 [149]
有些人认为当代所实施的这些商业性代孕与那次引发“婴儿M”案件的合同相比较,在道德上不是那么令人困惑了。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代孕者并不提供卵子,而只是提供子宫和怀孕的劳动力,因此,这个孩子在基因上并不是她的。根据这种观点,这里没有出售孩子一说,对孩子的索要也不太可能会遭到反对。
可是妊娠外包并没有解决这一道德困境。妊娠代孕者跟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也许真的不像提供卵子的代孕者与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联系得那样紧密。然而,将母亲这一角色划分成三种(养母、提供卵子者、妊娠代孕者)而非两种,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谁更有权利索要这个孩子。
如果说,因试管受精而产生的怀孕外包带来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使得这些道德问题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凸显。想要代孕的夫妇省下来的代孕费用,印度代孕母亲从这一行为中所获得的、与当地工资收入相差巨大的经济收益,让我们不可否认商业性的代孕可以增加整体福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很难反对这种作为全球化产业的有偿怀孕。
然而,这种全球化的怀孕外包同样也凸显了相关的道德困境。26岁的印度妇女苏曼·多蒂娅(Suman Dodia),曾是一对英国夫妇的代孕者。在此之前,她是一个女仆,每个月的收入是25美元。工作9个月就能挣4 500美元对她来说具有太强大的吸引力,而无法加以拒绝。 [150] 她曾经在家里生过三个自己的孩子,并且从来没有看过医生这样一个事实,增加了她作为代孕母亲的心酸。当谈到她的有偿怀孕时,她说:“我现在比我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还要小心。”尽管成为一个代孕母亲给她带来的经济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断定这个选择是自由的。此外,一个有偿怀孕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在贫困国家里受到目的明确的政策的驱使—反映出代孕通过将妇女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工具化,从而贬低了她们。
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生孩子和打仗彼此更为迥异的两种人类行为。但是,印度的那些代人怀孕的妇女们与安德鲁·卡内基在内战中雇用来代替他的士兵却有着共同之处。对这些情形的正当性的思考将使我们直面那两个将两种不同的公正观念区分开来的问题:我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到底有多自由?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德性和更高的善是无法在市场上受到尊重的,并且是金钱所不能购买的?
如果你相信普遍人权,那么你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如果所有的人都值得尊重,而无论他们是谁或在哪里居住,那么,把他们仅仅看做达到集体幸福的工具就是不对的。(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营养不良的、为了“城市的幸福”而在地窖里挣扎呻吟的孩子的故事。)
你可能基于这样的理由—尊重人权从长远来看将使功利最大化—而维护人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尊重人权的理由就不是为了尊重那些拥有权利的人们,而是为了使事物对每个人来说都变得更好。因为受折磨的孩子这一情景减少了总体功利而谴责这种情形是一回事,而因为它在道德本质上就是错的,是对这个孩子的不公正而加以谴责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权利并不依赖于功利,那么什么才是它们的道德基础呢?自由至上主义者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人们不应当被仅仅当做促进他人福利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因为这样做侵犯了根本性的自我所有权。我的生命、劳动力和人格属于我,且仅属于我。它们并不是任由社会整体随意处置的东西。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所有权的观念,如果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的话,那么它有一些后果是一个热切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才能喜爱的—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不给那些落后之人提供安全的防护网;一个放弃了任何缓和不平等和推进共同善的手段的最小政府;一种对自由的彻底赞颂,以至于它允许人们自行冒犯人类的尊严,如相互同意的吃人或把自己出售成为奴隶。
即使是拥护财产权利和有限政府的伟大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也不宣扬不受限制的自我所有权。他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可以如自己所愿地任意处置我们的生命和自由。可是洛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追溯到了上帝,这便给那些寻求不依赖于宗教设想的道德基础的人遗留了一个问题。
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为义务和权利提供了另一种可选的论证,这是迄今为止哲学家给出的最强有力、最有影响力的论证之一。它并不依赖于“我们拥有自身”这样的观念,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是来自于上帝的礼物”这样的主张。相反,它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
康德于172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市,大约80年之后,他也在那里去世。他来自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马具制造者,父母都是虔信派教徒,都是强调内在宗教生活和做善事的新教信仰者。 [152]
他16岁的时候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在校表现卓越。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私人家庭教师,然后在31岁的时候接受了第一份学术性工作—做一名没有工资的讲师,这份工作的报酬由参加讲座的学生人数而定。他是一个受欢迎的、勤奋的讲师,每周大约开20场讲座,主题囊括形而上学、逻辑、伦理学、法律、地理学和人类学。
1781年,在他57岁的时候,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该书对大卫·休谟和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四年之后,他发表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他诸多著作中的第一本道德哲学著作。在杰里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发表五年之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对功利主义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抨击。它认为,道德跟使幸福最大化以及任何其他目的无关,而在于将人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出现在美国革命(1776)爆发后不久,而又刚好在法国大革命(1789)爆发之前。与这些革命精神和道德驱动力相契合,这本书为18世纪的各种革命所倡导的人的权利以及21世纪初期我们所说的普遍人权,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基础。
康德的哲学是非常难懂的,但是别让这一点把你吓跑了。它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因为所获得的收益将颇为丰厚。《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它阐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自由?
康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后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影响深远。然而他的历史性的影响并不是我们关注他的唯一理由。虽然乍看起来,康德的哲学令人望而却步,但它实际上影响了当代人关于道德和政治的思考,即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因此,弄明白康德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训练,还是一种检验某些暗含于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关键性假设的方式。
康德对于人类尊严的强调影响了当今的普遍人权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自由的论证体现在当代人关于公正的争论当中。在本书的引言中,我区分了三种公正进路。那种功利主义的进路认为,界定公正和判断何谓正当之事的方法就在于询问什么将会使福利或社会总体幸福最大化。第二种进路将公正与自由联系起来,自由至上主义者为这一进路提供了例证。他们认为,关于收入和财富的正当分配就是任何一个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中自由交换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分配。他们坚持认为,调节市场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侵犯了个体的选择自由。第三种进路认为,公正就是给予人们在道德上所应得的—以分配物品来奖励和促进德性。当我们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时候(第八章),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基于德性的进路将公正与关于良善生活的反思联系了起来。
康德反对第一种进路(使福利最大化)和第三种进路(促进德性)。他认为,这两种进路都没有尊重人类自由。因此,康德是第二种进路—将公正与道德同自由联系起来—的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所提出的自由观念要求更为苛刻—比我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时所行使的选择自由要更加苛刻。康德认为,我们日常所认为的市场自由或消费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仅仅满足我们事先并没有选择的各种欲望。
稍后,我们将进入康德的那种更加崇高的自由观。然而,在我们进入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认为功利主义将公正和道德看做幸福最大化的观念是错误的。
康德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由于将权利建立在关于什么会产生最大幸福的算计的基础之上,功利主义使权利的基础变得脆弱。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试图从我们恰好具有的各种欲望推导出道德原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道德的方式。仅仅因为某物给很多人带来快乐,并不能使它成为正当的。仅仅根据大多数人(无论数量有多大)喜欢一种法律(无论有多强烈)的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使这个法律成为正当的。
康德认为,道德不能仅仅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考量之上—如人们在特定时间具有的各种兴趣、期望、欲望及偏好。他指出,这些因素是多变的、偶然的,因此它们很难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如普遍人权)的基础。可是,康德的根本性观点是,如果将道德原则建立在各种偏好和欲望—即使是对幸福的欲求—的基础之上,就误解了道德是什么这一问题。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对于确立道德而言毫无贡献,因为使一个人幸福不同于使他变好;使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变得审慎明智,不同于使他更有德性”。 [153] 将道德建立在兴趣和偏好基础之上,就破坏了它的尊严。它并不教导我们如何区分对与错,而“只是更加工于计算”。 [154]
如果我们的各种期望和欲望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一种可能性就是上帝,不过这并不是康德的回答。尽管康德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将道德建立在神圣权威的基础之上。相反,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他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而达到道德的最高原则。根据康德的观点,要弄明白我们如何能推理出道德法,就要先探索我们的理性能力和自由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
康德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即能够进行推理;我们也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能够自由地行动和选择。
康德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理性地行动或自主地选择。有时候我们可以,而有时候却不能。他的意思是我们有理性的能力和自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人类所共有的。
康德毫不犹豫地承认理性能力并不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一种能力,我们还有感觉快乐与痛苦的能力。康德认识到,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感性的存在。康德所说的“感性”是指,我们能够基于自己的感官和感觉行事。因此,边沁是对的—但是只对了一半。边沁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喜欢快乐而讨厌痛苦;然而,他错在坚持认为它们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康德认为,理性可以是最高统治者,至少在某些时候如此。当理性掌管我们的意志时,我们就不受欲望的驱动去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我们的理性能力与自由能力密切相关,这些能力合起来让我们变得独特,并将我们与动物性存在区分开来;它们使我们不仅仅是欲望的存在。
要弄明白康德的道德哲学,我们就需要理解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经常将自由看做毫无障碍地做我们想做之事,对此,康德并不同意。他有一个更加严格的、要求更为苛刻的自由观念。
康德的推理如下:当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时,我们并不是真正自由地行动,而是作为欲望和渴求的奴隶而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是在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某种外在于我们的目的。我以这种方式来充饥,以那种方式来解渴。
假设我正在试着决定买哪一种口味的冰激凌:我是应该买巧克力的呢,香草的呢,还是咖啡太妃糖颗粒的呢?我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运用选择的自由,但是,我真正在做的只是在试着弄明白哪一种口味能最好地满足我的偏好—那些我事先并没有加以选择的偏好。康德并没有说满足我们的各种偏好是不对的,他的要点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自由地行动,而是在根据一种外在给定的规定性而行动。毕竟,我对咖啡太妃糖颗粒的偏好而不是对香草的偏好并不是我刻意去选择的—我就是有这个偏好。
若干年以前,雪碧有一句广告语:“服从你的渴望”(Obey your thirst)。雪碧的这一广告(当然是无意地)包含了一种康德式的洞见。当我拿起一罐雪碧(或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时,我是出于服从而不是自由在行动。我只是在服从我的口渴感。
人们经常就本性和后天培育在行为养成中的作用而进行争论,想要雪碧(或其他含糖饮料)的欲望是内含于基因之中的呢,还是受到广告的刺激?对于康德来说,这一争论实际上偏离了重点。只要我的行为被生物性所决定,或被社会性所规范,那它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一种理解康德所说的“自律地行动”的途径,就是将意志自由与其对立面作比较。康德发明了一个词来表达这一对比—他律(heteronomy)。当我根据他律而行动的时候,我就是在根据那外在于我而给定的规定性而行动。举个例子:当你丢下一个台球时,它会落到地上;当它下落的时候,它并不是在自由地行动,其行动受到自然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地球引力—的支配。
假设我从帝国大厦上跌落(或被推下),当我冲向地面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我在自由地行动;我的行动与那个台球一样,受制于地球引力这一法则。
现在再让我们假设,我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并且砸死了那个人,我不会对这一不幸死亡负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就像那个台球,如果它从高处跌落并砸到某个人的脑袋,它也不会对此负有道德责任。在这两种情况中,那正在下降的物体—我,或者那个台球—都不是在自由地行动,而是都受制于地球引力这一法则。由于这里没有意志自由,那么也就没有道德责任。
这就是意志自由和康德的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自由地行动并不是为给定的目的选择最佳的方式,而是选择目的本身—这是一种人类可以做出,而台球(以及大多数动物)却不能做出的选择。
现在是凌晨三点,你的大学室友问你为什么深夜不睡觉,而是思考与失控电车有关的道德困境。
“为了给伦理课写一篇好论文。”你回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写一篇好论文呢?”你的室友问道。
“为了获得一个好成绩。”
“可是为什么要在乎成绩呢?”
“为了在投资银行得到一份工作。”
“可是为什么要在投资银行得到一份工作呢?”
“为了某天成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
“可是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呢?”
“为了赚很多的钱。”
“可是为什么要赚很多的钱呢?”
“为了能够经常吃龙虾,我喜欢吃龙虾。毕竟,我是一个有感知的生物。这就是我为什么熬夜思考失控电车的原因!”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规定性”的一个事例—做某事是为了其他事情,再为了其他事情,如此等等。当我们他律地行动时,我们是为了某些外在于我们的给定的目的去行动,我们是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的设定者。
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与此截然对立。当我们自律地行动—也即根据我们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时—我们做某事是为了这件事本身,它自己就是目的。我们不再是那些外在于我们的给定的各种目的的工具。“自律地行动”这一能力,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它标示了人和物之间的区别。
对于康德而言,尊重人的尊严就意味着将人当做目的本身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功利主义为了总体福利而利用人是不对的。将那个大汉推落到轨道上以挡住电车,就是把他当做了工具,因此就没有把他当做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一个开明的功利主义者(如密尔),可能会出于对次生效益的考虑—即从长远来看会降低功利—而拒绝去推那个人。(比如人们将不敢站在桥上了,等等。)然而,康德会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让人打消推人下桥的念头的理由,它仍然是将那个潜在的受害者当做成全他人幸福的一种工具、一个对象、一种手段。它让他活着,却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让他人以后在过桥时不会再三犹豫。
这引发了一个关于“什么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的问题,它将我们从康德的那种特殊的、要求苛刻的自由观,带到了那同样要求苛刻的道德观。
根据康德的理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重要的是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因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做这件事,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隐晦不明的动机去做它。
“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康德写道。它本身就是好的,而无论它是否盛行。“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整价值的事物一样。” [155]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道德上的善的事物而言,“它应当遵守道德法这一点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而被完成。” [156] 那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的动机,就是履行义务的动机;后者在康德这里是指为了正当的理由而做正当之事。
在论及只有义务的动机才能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的时候,康德并不是在谈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特殊义务,他也不是在告诉我们那最高道德原则所命令的是什么。他不过是在说明当我们评价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时,我们要评价产生这一行为的动机,而不是它产生的后果。 [157]
如果我们是出于某些动机—如自我利益—而不是义务去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就缺乏道德价值,康德坚持认为这是真实的,这一点不仅仅是针对自我利益而言,也是针对所有企图满足我们的各种期望、欲求、偏好和渴望的行为而言。康德将这样的动机—他称之为“倾向的动机”—与义务的动机作了对比,并且认为,只有出于义务动机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
康德举出了很多事例以说明义务和倾向之间的区别。第一个事例是关于一个慎重的店主的。一个毫无经验的顾客(例如一个孩子)走进一家杂货店买一袋面包,店主可以多要他的钱—向他索要比通常一袋面包的价格要高的钱,而且这个孩子对此并不知情。可是这个店主意识到,如果有其他人发现他以这样的方式占这个孩子的便宜,那么这件事就会传播开来,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出于这个原因,他决定不多收这个孩子的钱,而是按通常的价格收费了。因此,店主做了正确的事情,然而却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他诚实地与这个孩子做生意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保护他的名声。店主只是为了自我利益才诚实地行动,他的行为缺乏道德价值。 [158]
我们可以在纽约商业促进会的招募活动中发现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事例。为了征召新成员,商业改进局经常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并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利可图的”为标题。这则广告的内容毫无争议地表达了它所诉求的动机:
诚实,与任何其他财富一样重要。因为一场以真实、开放和公平价值为基础的交易,不会做不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支持商业促进会。加入我们吧,你可从中获益。
康德不会谴责商业促进会,促进诚实的商业交易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在为了诚实而诚实与为了底线而诚实这两者之间有重要的道德差别。前者是一种原则性的立场,而后者则是一种慎重的立场。康德认为,只有原则性的立场才与义务的动机相一致,而义务的动机是唯一能够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的动机。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例子:若干年以前,马里兰大学试图通过要求学生签署不作弊的保证书,以解决普遍存在的作弊问题。作为一种鼓励,那些签署保证书的学生得到了一张打折卡,他们凭这张卡在当地商店消费可以节省10%~25%的花费。 [159]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学生是为了当地比萨店的折扣而承诺不作弊。可是,我们大多数人会同意,收买诚实这一行为缺少道德价值。(这些折扣可能成功地减少了作弊的发生率,也可能没有;然而,这里的道德问题是,被对折扣或物质奖励的欲求所推动的诚实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对这一疑问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这些例子体现出康德的主张的合理性,他认为只有义务的动机—因为某事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便利的而去做它—才能给一个行为赋予道德价值。可是,另外有两个例子却体现了康德这一主张的复杂性。
正如康德所认为的,第一个例子涉及保存一个人自己生命的义务。由于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活下去的意向,因此,这一义务很少起作用。我们用以维持生命的大多数预防措施,由此都缺乏道德含量。系上座位安全带和控制我们的胆固醇等,都是一些慎重的行为,而并非道德的行为。
康德承认,我们经常很难知道,当人们行动的时候是受到什么动机的驱使。他也认识到,义务的动机和倾向可能都存在。他的意思是:只有义务的动机—因为某事是正当的而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或便利的而去做—才能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他用自杀的例子来阐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人之所以活下去是因为他们热爱生命,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康德提出了一种事例,其中义务的动机进入人们的视野。他假设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悲惨可怜的人,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以至于他没有任何继续生存的欲望。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出于义务而不是出于意向来振奋意志以维持生命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 [160]
康德并不是认为只有悲惨的人才能履行维持自己生命的义务。我们很有可能热爱生命并仍然为了正确的理由—一个人有义务这样做—而维持生命。假如一个人认识到那种维持自己生命的义务,并在心里出于这一理由而这样做了,那么,那种想要继续生存的欲望就并没有破坏维持生命的道德价值。
可能对康德的观点而言,最难论证的例子就是如何看待帮助他人这一义务。有些人是利他主义的,他们同情他人并从帮助他人中获得乐趣。然而,对康德而言,出于同情而做好事,“无论它多么正当,也无论它多么友善”,都缺乏道德价值。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难道成为那种在帮助他人中获得乐趣的人不好吗?康德会说好。他当然不会认为,出于同情而行动有什么错;但是他将这种帮助他人的动机—做好事给我带来快乐—与义务的动机区分开来,并且坚持认为,只有义务的动机才能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利他主义者的同情,“值得我们称赞和鼓励,但不值得尊敬”。 [161]
那么,一件好事要想具有道德价值的话,要具备什么呢?康德提出了一种情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利他主义者遭受了一种不幸,使他对于人类的爱不复存在。他变成了一位恨世者,缺乏所有的怜悯和同情。然而,这个冷心肠的人将自己从冷漠中扯了出来,并着手帮助他的同胞。由于没有任何帮助的倾向,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义务”。那么,他的行为才第一次具有了道德价值。 [162]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古怪的评判。康德有意要把厌恶人类者界定为道德榜样吗?不,一点儿也不是。从做好事中获得乐趣,并不一定破坏其道德价值。康德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做某件好事是因为它是正当之事—而无论这样做是否给我们带来快乐。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事情: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全国拼字大赛”上,一个13岁的男孩被要求拼写“echolalia”,意指一个人重复任何他所听所闻的倾向。尽管他拼错了这个单词,可是考官也听错了。考官告诉他拼对了,并允许他晋级。当男孩得知自己拼错了之后,他走到考官面前告诉了他们。后来他被淘汰了。第二天,报纸头条称赞这个诚实的年轻人是“拼字大赛的英雄”,他的照片也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考官们说我非常正直。”男孩告诉记者说,并接着说他的部分动机是“我不想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讨厌的人”。 [163]
当我读到拼字大赛英雄的这段话时,我很好奇康德会怎样想。不想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讨厌的人,这当然是一种倾向。因此,如果这是他说实话的动机,那么,这就似乎诋毁了他这一行为的道德价值。可是这似乎太苛刻了。这可能意味着,只有没有感觉的人才能做出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我认为这并不是康德的本意。
如果这个男孩说实话的唯一理由就是避免感到罪恶,或避免万一他的错误被发现后而导致的坏名声,那么,他说实话这一行为就缺乏道德价值。然而,如果他说实话的原因是他知道这是正当之事,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不管那可能与之相随的快乐或满足。只要他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而做了正当的事情,那么,对这件事情的良好感觉,就并没有抵消它的道德价值。
康德的利他主义者也是如此。如果他帮助他人,仅仅是为了这样做所给他带来的快乐,那么,他的行为就缺乏道德价值。然而,如果他认识到一种帮助人类同胞的义务,并且出于这种义务而行动,那么他从这种行为中所获得的快乐在道德上就不能说是不合格的。
当然,在实际中,义务和倾向经常同时存在。我们经常很难弄明白自己的动机,更不用说确切地知道他人的动机。康德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也并不是认为只有硬心肠的厌恶人类者才能做出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他那个厌恶人类者的例子的要点在于,要将义务的动机孤立开—要确保它不被怜悯和同情遮蔽。一旦我们看到了义务的动机,我们就能甄别良善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赋予这些行为以道德价值—也即它们的原则,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如果道德意味着出于义务而行动,那么,我们仍然要说明义务由何构成。对康德而言,要弄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要弄明白道德的最高原则。那么,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什么呢?康德写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弄明白康德是如何将三个重要的观念—道德、自由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接近他的答案。他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和二元论来解释这些观念。它们涉及一些晦涩难懂的术语,不过如果你注意到这些截然不同的术语中的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你就能很好地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了。以下是一些需要记住的对比:
对比1(道德):义务 Vs. 倾向
对比2(自由):自律 Vs. 他律
对比3(理性):绝对命令 Vs. 假言命令
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些对比中的第一种—义务和倾向之间的对比,只有出于义务的动机才能赋予一个行为以道德价值。现在来看看我是否能够解释其他两个。
第二种对比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可以决定我们的意志的方式—自律和他律。根据康德的思想,只有当我的意志是被自律所决定、受我自己给定的法则所支配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再者,我们经常将自由看做能够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不受阻碍地追求我们的欲望。然而,康德向这种思考自由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挑战:如果你没有首先自由地选择这些欲望,那么,在你追求它们的时候,又怎么能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呢?康德在自律和他律这一对比中,表述了这一挑战。
当我的意志被他律所决定时,它是被外在地、从我之外而决定的。然而这就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自由意味着不只是服从我的欲望和倾向,这又如何可能呢?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都是受那些欲望或倾向—它们由外在影响而决定—所推动的吗?
对此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康德论述道:“自然中的任何事情都符合于法则。”如自然中必然性的法则、物理规律以及因果律。 [164] 这也包括我们自身。我们毕竟是自然的存在,人类并不豁免于自然定律。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掌控自由,我们就必须能够根据某些其他种类的法则—并非物理规律—而行动。康德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这种或那种规律所支配的。如果我们的行为仅仅受物理规律的支配,那么我们与那个台球就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掌控自由,我们就必须能够不根据那给予我们或强加给我们的法则而行动,而是根据我们给自己所定的法则而行动。可是,这种法则又从何而来呢?
康德对此的回答是:由理性而来。我们不仅是受感官所产生的快乐与痛苦支配的感性存在,同时也是理性的存在,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决定我的意志,那么,这种意志就会成为一种不受自然或倾向所支配而进行选择的力量。(我们要注意到,康德并不是在断言,理性总是支配我的意志;他只是在说,当我能够自由地行动—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那么,这肯定就是那种“理性能够支配我的意志”的情况。)
当然,康德并不是第一位认为人类具有理性的哲学家。然而,他的理性观念,就像他的自由观、道德观一样,都是极其苛刻的。对于经验主义哲学家们(包括功利主义者)来说,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使我们能够甄别追求各种特定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不是理性本身规定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理性称为“对欲望的寻求”,大卫·休谟将理性称为“激情的奴隶”。
功利主义者们认为人类具有理性能力,但仅仅是工具理性能力。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理性的工作并不在于去决定什么样的目的是值得追求的,而在于弄明白,怎么样通过满足那些我们恰好具有的各种欲望,而使功利最大化。
康德反对理性的这种附属性角色。对他而言,理性并不仅仅是激情的奴隶。康德说,如果这就是理性,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只保留本能。 [165]
康德的理性观念—与道德有关的实践理性—并不是工具性的理性,而是“纯粹实践理性,它忽视所有的经验目的而设定了一种先验性”。 [166]
可是,理性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康德区分了两种理性能够命令意志的方式,两种不同的命令。一种命令—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那种—就是假言命令。假言命令运用的是工具理性:如果你想要X,那么就做Y。如果你想要一个良好的商业声誉,那么就要诚实地对待你的顾客。
康德将假言命令(总是有条件的命令)与那种无条件的命令(绝对命令)作了对比。“如果一个行为,只是在作为一种达到其他事物的手段时才是好的,”康德写道,“那么,这一命令就是假言命令。如果这个行为本身就代表着善,并因此对意志—这种意志自身符合于理性—来说非常必要的话,那么这一命令就是绝对的。” [167] “绝对”这一术语看起来像晦涩难懂的术语,但它并不是那么远离于自身的日常意义。康德的“绝对”意思是指“无条件”。举个例子,当一名政治家对自己所谓的丑闻发表一个绝对的否认的时候,那么这一否认就不仅仅是强调性的,同时它还是无条件的—不存在任何漏洞和例外。同样的,一个绝对义务或绝对权利,就是一个无视各种环境而普遍适用的义务或权利。
对于康德而言,一个绝对命令就是绝对地—不涉及或依赖于任何进一步的目的—发出命令。“它与这个行为的内容及其预期目的无关,而与这个行为的形式以及那产生这一行为的原则有关。这一行为中的本质性的善在于意图,而无论结果如何。”康德论证道,只有一个绝对命令才有资格作为一种道德命令。 [168]
这三种并列的对比之间的关联,逐渐浮出水面。要想获得自律意义上的自由,就需要我并不是出于一个假言命令去行动,而是出于绝对命令去行动。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什么是绝对命令呢?它又命令我们什么呢?康德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观念—一项绝对的、不带任何进一步的动机而自主命令的实践法则 [169] —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依据那种使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而联合起来的法则的观念,而不管具体目的—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康德提出了若干版本或形式的绝对命令,他认为这些都是绝对命令。
康德将第一种形式称为普遍法的准则:“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170] 康德所说的“准则”是指一种给予你的行动以理由的规则或原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们应当仅仅依据那些我们可以使之毫无矛盾地普遍化的原则而行动。为了弄明白康德的这种不可否认的抽象考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具体的道德问题:做出一个你知道自己不会遵守的承诺是对的吗?
假设我现在急需钱,因此想找你借一笔。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近期内无法偿还,那么,我通过做出一个虚假的承诺说将很快偿还这笔钱—一个我知道我无法遵守的承诺—而得到这笔借款,这在道德上是否允许呢?一个虚假的承诺与绝对命令是否一致呢?康德说不,显然不一致。我看清这一虚假承诺与绝对命令不一致的途径是:试着将我即将赖以行为的准则普遍化。 [171]
在这一情形中,准则是什么呢?好像是这样的东西:“无论何时,当一个人急需钱的时候,他应当借款并承诺还款,即使他知道自己并不能还。”康德说,如果你将这一准则普遍化并与此同时根据它而行动,那么你就会发现一种矛盾:如果每个人在需要钱的时候都做出虚假的承诺,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实际上,将会没有“承诺”这种东西;将这种虚假的承诺普遍化会破坏“遵守诺言”的这一习俗。届时你试图通过承诺而获得一笔钱的尝试将是徒劳的、非理性的。这表明,做出虚假的承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与绝对命令不一致。
有些人会发现康德这种形式的绝对命令并不具有说服力。这种普遍法的准则与成年人谴责那些插队、不合时宜地说话的孩子们时所用的道德陈词滥调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呢?”如果每个人都说谎,那么没有人会相信其他人的话,我们也都将更加糟糕。如果这是康德的意思,那么,他最终也就是在作一种结果主义的论证—并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虚假的承诺,而是因为其可能具有的有害效果或后果而反对之。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思想家,对康德提出了这一批评。然而,密尔误解了康德的意思。对于康德而言,弄明白我是否能够将自己的行为准则普遍化并继续依据它而行动,并不是一种推测可能性结果的方式。它是一种考察,以弄明白我的准则与绝对命令是否相一致。一个虚假的承诺,在道德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它明显会破坏社会诚信(尽管它会这样)。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在做出这样一个虚假承诺时,我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金钱的欲望)置于他人的需要和欲望之上。这种普遍化的考察表明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主张:这是一种检验的方式,它力求弄明白—我即将做出的行为是否将我的利益和特殊情况置于他人的之上。
绝对命令的道德力量在康德的第二个绝对命令的准则—将人看做目的—当中,显现得更加清楚。康德这样提出他的第二种绝对命令:我们不能将道德法则建立在任何特殊的利益、意图或目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将仅仅与那些目的的拥有者相关联。“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它们是一些其存在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作为目的本身,“那么在其中—仅仅在其中,就会有一个可能的绝对命令的基础”。 [172]
什么作为目的本身会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呢?康德的答案是—人性。“我认为,每一个人—一般来说就是每一个理性存在—都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而不仅仅是这种或那种意志所任意使用的手段。” [173] 康德提醒我们,这是人和物之间根本性的区别。人是理性的存在,他们不仅具有一种相对价值,而且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一种本质性的价值。也就是说,理性存在拥有尊严。
这种论证路线引导康德达到了第二种形式的绝对命令:“应当这样行为:不要总是将人—无论是你自己本身还是任何其他人—仅仅看做一种手段而加以对待,而总是同时也把他们看做一种目的而加以对待。” [174] 这就是将人作为目的的准则。
让我们再一次考虑一下那个虚假的承诺。绝对命令的第二种形式帮助我们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看明白,它为什么是错的。当我承诺说我会把钱还给你,而又知道自己并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在利用你。我将你作为我经济上的偿还能力而加以利用,并不是将你看做一个值得尊重的目的而加以对待。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自杀的情形。我们注意到,有意思的是,谋杀和自杀都是与绝对命令相抵触的,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从道德上来看,我们经常将谋杀和自杀看做完全不同的行为。将他人杀死是违背他的意志而剥夺了他的生命,而自杀是自杀者自己的选择。然而康德的“将人看做目的”这一观念,将谋杀与自杀放在同等地位上了。如果我实施了谋杀行为,我就是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如抢劫银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发泄我的愤怒之情—而夺走了某个人的生命。我将这个受害者当做一种手段加以利用,而没有将他的人性当做目的而加以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谋杀违背了绝对命令。
对于康德而言,自杀以同样的方式违背了绝对命令。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我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就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然而康德提醒我们,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被仅仅当做手段而加以利用的东西”。我没有权力舍弃那内在于自己的人性,就像我没有权力舍弃那内在于他人的人性一样。对于康德来说,自杀与谋杀之所以错误的原因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将人看做物而加以对待,都没有将人性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 [175]
自杀的例子,凸显了康德所说的“尊重我们人类同胞之义务”的显著特征。对于康德而言,自尊和尊重他人源自于一个并且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对于理性存在的人,对于人性的载体,负有尊重的义务。它与这个人实际上是谁并无关系。
在尊重和其他形式的人类情感之间,有不同之处。爱、同情、团结以及同胞情感都是道德情感,它们将我们与一些人拉得比另外一些人更加亲密。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因与任何关于它们的特殊事物无关。康德式的尊敬不同于爱,不同于同情,也不同于团结或同胞情感。这些关心他人的原因,与他们具体是谁有关。我们爱自己的配偶以及家庭成员,我们同情那些我们能够认出的人,我们与朋友和同志感觉到团结。
然而康德式的尊敬是尊敬这样一种人性,尊敬一种内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的、毫无差别的理性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的情形中侵犯它与在他人的情形中侵犯它是同样值得反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德式的尊敬原则适合于普遍人权的学说。对于康德而言,公正要求我们支持所有人的人权,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们与他们有多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
现在我们可以弄明白康德所说的那种道德和自由之间的联系了。有道德地行动意味着出于义务—为了道德法则—而行动。道德法则由一个绝对命令所构成,也即一个要求我们尊敬地将他人当做目的本身而加以对待的原则。只有当我的行为与这个绝对命令相一致的时候,我才是自由地行动。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依据一个假言命令而行动的时候,我都是为了某些外在于我而给定的利益或目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的意志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由我的环境需要或我恰好拥有的各种期望和欲求所决定的。
我只有自律地行动—根据我为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我才能脱离于本性和环境的命令。这样一种法则,必须不受到我的特殊期望和欲求所制约。因此,康德的要求苛刻的自由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相互关联的。自由地行动—亦即自律—与有道德地行动、遵从绝对命令地行动,是一回事。
这种思考道德和自由的方式,促使康德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那种将道德建立在某些特殊的利益或欲望(如幸福或功利)基础之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所发现的从来都不是义务,而只是出于某一特定利益而行动的必要性。”然而,任何基于利益的原则都“注定总是一个有条件的原则,而不可能作为一个道德法则”。 [176]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然而,人们却很难掌握它,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跟随着我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想到若干疑问。以下就是四个特别重要的疑问:
疑问1: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我们尊敬地对待每一个人,把他们当做目的本身而加以对待。这与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7) )是不是非常相似呢?
回答 :不。黄金法则依赖于这样一个偶然性的事实,即人们愿意怎样被对待。绝对命令要求我们从这些偶然性当中抽象出来,并将人们当做理性存在而加以尊重,无论他们在某一特殊的情境中可能想要什么。
假设你得知,你的兄弟死于一场车祸,而你住在养老院里的年迈体弱的母亲又向你询问他的近况。你在告诉她事实和不让她承受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震惊和痛苦之间,无从选择。何谓正当之事呢?黄金法则会询问:“在类似的情形中,你愿意被怎样对待呢?”答案当然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宁愿人们在他脆弱的时候,对他隐瞒残酷的事实;而有些人则想知道真相,无论有多痛苦。你可能会很好地推断,如果你自己置身于你母亲的情境之中,你宁愿人们不告诉你。
然而,对于康德而言,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重要的不是你(或你的母亲)在这些情形中会有什么感觉,而是将人当做值得尊敬的理性存在而加以对待,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情形中,同情可能与康德式的尊敬分道扬镳。从绝对命令的角度来看,出于关心她的感受而对她撒谎,就可以说是将她当做满足她自己的一种手段,而没有把她当做一个理性存在而加以尊重。
疑问2:康德似乎在暗示,对义务的回应与自律地行动是一回事。可是这如何可能呢?依据义务而行动就意味着不得不遵守一项法则。可是,服从于一项法则怎么可能与自由相一致呢?
回答 :义务与自律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中才相匹配:即,当我是我有义务去服从的法则的设定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尊严,并不在于我是道德法则的主体,而在于是“这一法则的设定者……并仅仅在此基础上服从于它”。当我们遵守绝对命令时,我们是在遵守一项自己所选择的法则。“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于其制定普遍法则的能力,尽管条件是他也要遵守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则。” [177]
疑问3:如果自律就意味着根据我自己给定的法则而行动,那么,什么能保证每个人都会选择同样的道德法则呢?如果绝对命令是我的意志的产物,那不是很可能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绝对命令吗?康德似乎认为,我们都会认同一样的道德法则,可是,他怎么能够确定,不同的人不会经由不同的推理并达到各种各样的道德法则呢?
回答 :当我们在命令道德法则时,我们并不是作为自己所是的特殊的个人,如你、我而进行选择,而是作为理性的存在,作为康德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参与者进行选择。因此,那种认为道德法则取决于作为个体的我们的观念是错误的。当然,如果我们从自己特殊的利益、欲望和目的进行推理,那么,我们可能会被引导至众多的原则。然而,这些并不是道德原则,而只是一些慎重的原则。当我们运用纯粹实践理性时,我们便抽象于自己的各种特殊利益。这就意味着,每个运用纯粹实践理性的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都会达到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绝对命令。“因此,一个自由的意志,与一个遵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同一回事。” [178]
疑问4:康德认为,如果道德不仅仅是一种慎重的算计,那么它就必须采取一种绝对命令的形式。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得知,道德独立于权力和利益的作用而存在呢?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我们拥有那种带着意志自由而自律地行为的能力呢?如果科学家们发现(如通过脑成像或认知神经科学)我们根本就没有意志自由呢?这会不会否定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呢?
回答 :意志的自由并不是科学所能证明或否定的东西,道德也同样不是。人类确实是居住于自然王国,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从一种物理的或生物的角度加以描述。当我举手投上一票时,我的行为可以通过肌肉、神经细胞、神经元的突触以及细胞而得到解释;然而,它也可以通过思想和信念而得到解释。康德说,我们不得不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自身—物理的和生物的经验王国,以及一种自由人类主体的“理智”王国。
为了更加充分地解答这一问题,我需要多说一些与这两种立场有关的内容。它们是我们看待人类主体,以及那些支配我们行为的法则的两种角度。以下便是康德对这两种立场的叙述:
一个理性的存在……有两种立场,从中他可以关注到自己,也可以知道那些支配他的所有行为的法则。他可以认为自己首先服从于自然法则(他律)—只要他属于这个感性世界;其次服从于这样的法则—只要他属于理智世界:该法则独立于自然,它并非经验性的,而只以理性作为基础。 [179]
这两种视角的对立关系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三种对比串联起来:
对比1(道德):义务 Vs. 倾向
对比2(自由):自律 Vs. 他律
对比3(理性):绝对命令 Vs. 假言命令
对比4(立场):理智王国 Vs. 感性王国
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我属于感知世界,我的行为由自然法则和因果规律而决定,这是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神经科学所能描述的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理性存在,我居住在理智王国。在这里,由于独立于自然法则,我能够自律,能够根据我给自己所设定的法则而行动。
康德坚决主张,只有从这第二种(理智的)角度,我才能把自己看做自由的,“因为独立于感知世界各种原因的支配(这也是理性必须总是归功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自由。” [180]
如果我仅仅是一个经验性的存在,那么我就不能自由;每一次意志的运用,都要受到某些利益或欲望的制约。所有的选择都将是他律性的选择,受制于对某种目的的追求。我的意志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第一原因,而仅仅是某种先在的原因的结果,是这种或那种冲动或倾向的工具。
只要我们将自己看做自由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自己只看做经验性的存在。“当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转化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并且认识到意志的自律及其结果—道德。” [181]
因此—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绝对命令如何可能?仅仅是因为“自由的观念使我成为理智世界的一员”。 [182] 我们能够自由地行动、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肩负道德责任,以及能够主张他人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观念,要求我们从这一角度—从主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客体的角度—来看待自身。如果你真的想抵触这一观念,并主张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完全只是幻觉,那么康德的论证并不能证明你是错的。然而,如果没有某些自由和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就很难—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理解我们自身以及弄明白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任何这样的观念,都将我们置于两种立场之中—主体的立场和客体的立场。一旦你明白了这种情形的力量,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科学永远都不能证明或否定自由的可能性。
要记住,康德承认我们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我们不仅仅居住于理智世界。如果我们仅仅是理性存在,不受自然法则和自然需要的制约,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将始终与自律的意志相一致”。 [183] 由于我们同时栖居于两种立场之中—必然的王国和自由的王国—所以在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应当做的之间,在事物所是的方式与它们所应当是的方式之间,就总是存在有一个鸿沟。
另一种表述这一要点的方式,就是认为道德不是经验性的,它总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对这个世界进行评判。科学尽其所有的力量与洞见,都不能触及道德问题,因为它是在感知领域起作用。
“要论证自由并不存在的话,”康德写道,“这对于最深奥的哲学以及最普通的人类理性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184] 康德很可能还会补充说,对于认知神经科学来说,无论它怎样先进发达,也是不可能的。科学能够研究自然,能够考察经验世界,可是它不能回答各种道德问题或推翻意志自由。这是因为,道德和自由并不是经验性的概念。我们不能证明它们存在,然而没有它们,我们也不能弄明白我们的道德生活之意义所在。
探索康德道德哲学的途径之一,就是弄明白他是如何将它应用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我想考虑康德道德哲学的三种应用—性、谎言与政治。哲学家们在怎样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这一方面并不总是最高权威。然而,康德所举的实例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有趣的,并能体现出他整个的哲学体系。
康德对于性道德的观点是传统而保守的。除了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之外,他反对任何一种可以想象的性行为。“康德关于性的观点是否源自于他的道德哲学”这一问题,并没有这些观点所反映出的那种潜在性的观念重要,这个潜在性的观念就是:我们并不拥有自身,也不任由自己随意支配。他基于这样的理由而反对随意性行为:随意性行为—他意指婚外性行为—无论双方是否同意,对双方来说都是贬低性的、对象化的。他认为,随意性行为是值得反对的,因为它完全是性欲的满足,而不是尊重伙伴的人性。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他对她作为一个人并不关心,只有她的性才是他所欲求的对象。 [185]
即使当随意性行为涉及伙伴双方的相互满足时,“他们当中的一方也玷污了另一方。他们将人作为满足他们的性欲和倾向的工具”。 [186] (康德认为婚姻通过使性行为超越了生理的满足并将它与人的尊严相联系,从而升华了性行为。究其原因,我们稍后将讨论。)
在转而讨论卖淫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一问题时,康德质问道,在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性能力的使用与道德相符合。他的回答是—在此处与在别的情境中的回答一样—我们不应当将他人或我们自己仅仅当做对象。我们并不能任由自己随意支配。与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观念截然相反,康德坚持认为,我们并不拥有自身。“我们要将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加以对待”的这一道德要求,限制了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我们自己的方式。“人不能随意支配自己,因为他不是物,他并不是自己的财产。” [187]
在当代关于性道德的各种争论中,那些援引意志自由权利的人认为,个人应当能够自由地选择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然而这并不是康德所说的意志自由的意思。似乎矛盾的是,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给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增加了某些特定的限制。例如,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意志自由就意味着我受制于我给自己所订立的法则—绝对命令;而绝对命令要求我郑重地将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当做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而加以对待。因此,对康德而言,按照意志自由行动,要求我们郑重地对待自己,而不是使我们自己对象化。我们不能以任何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
肾交易市场在康德那个时代并没有盛行,但富人确实可以从穷人那里购买牙齿以进行移植。[《牙齿移植》是18世纪英国漫画家托马斯·罗兰逊(Thomas Rowlandson)所画的一幅漫画,它展示了某牙医医务室内的一个场景:一名外科医生正从一个扫烟囱的工人的嘴里拔牙,而一些阔太太则在一旁等候着移植。]康德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一个人“没有资格出售自己的四肢,甚至没有资格出售自己的一颗牙齿”。 [188] 这样做就是将自己看做一个对象,一个手段,是谋取利益的工具。
康德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反对卖淫。“为了利益而允许被他人用来满足性欲、将自己作为一种需求的对象,就是……将自己当做一个物体,以使得另一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其肉体欲望,就像他用牛排来充饥一样。”人类“没有权利为了利益而使自己成为供他人满足其性倾向的物体”。这样做,就是将一个人仅仅当做物,一个可供使用的对象。“这里潜在性的道德原则是:人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也不能随其所愿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189]
康德对卖淫和随意性行为的反对,体现出他所认为的意志自由—一个理性存在的意志自由—与个体出于同意的行为之间的对比。我们通过运用意志而达到的道德法则,要求我们永远不能将(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人性仅仅当做手段,而是要当做目的本身加以对待。尽管这一道德要求基于意志自由,它却排除了达成同意的成人之间的某些行为,也即那些与人类尊严和自尊不一致的行为。
康德总结道,只有婚内性行为才能避免“贬低人性”。只有当两个人将自己完全交给对方,而不是仅仅将自己性能力的使用交给对方时,性行为才不是对象化的。只有当伴侣双方互相分享他们“无论好坏以及各方面的人、身体和灵魂”时,他们的性行为才能导致“一种人与人的联合”。 [190] 康德并没有说,每一个婚姻在实际上都产生了这种联合。他也有可能错误地认为,婚外就永远不会发生这种联合,或婚外性关系除了性满足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然而,他关于性的观点,却体现了当代争论中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两种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不受约束的同意的伦理,和尊重意志自由以及人的尊严的伦理。
康德坚决反对撒谎。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撒谎被作为不道德行为的一个主要例子。然而,让我们假设一下,一个朋友正躲在你家里,而一个杀人犯来到你家门口找他。此时对杀人犯撒谎难道不对吗?康德说不对。说真话的义务保持不变,而无论结果如何。
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是一位与康德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他对这种毫不妥协的立场提出异议。贡斯当认为,说真话的义务仅仅适用于那些应该得知真相的人,而这个杀人犯肯定不应该得知真相。康德回应道,对这个杀人犯撒谎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这伤害了他,而是因为这违背了正当性的原则:“不能避免表达的真实性,这是每个人的正式义务,无论这会对他或任何他人产生怎样的不利。” [191]
不可否认的是,帮助一个杀人犯去实现他的邪恶行为,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然而,请记住,对康德来说,道德并不是关于结果的,而是关于原则。你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在这一情形下即为说实话—的结果,因为结果是与偶然性绑定在一起的。你可能不会知道,由于害怕这个杀人犯会过来,你的朋友已经从后门溜出去了。康德论述道,你必须说真话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杀人犯有权利得知真相,或者谎言会伤害他,而在于一个谎言—任何谎言—“都损害了正当性的真正来源……因此,在所有的陈述中都要真实(诚实),是理性的一种神圣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它不允许有任何权宜之计”。 [192]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而极端的立场。我们当然没有道德义务来告诉一个纳粹党突击队员说,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及其家人正藏在阁楼上。似乎康德坚持对门口的杀人犯说实话的这种要求,要么是错误地应用了绝对命令,要么就证明了绝对命令很愚蠢。
尽管康德的主张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可我还是想为之稍作辩护。尽管我的辩护与康德所提供的辩护不太一样,它却本着康德哲学的精神气质,并且,我希望能够凸显康德的哲学。
想象一下你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之中:一个朋友躲在衣橱里,而杀人犯就在门口。你当然不想帮助杀人犯实现他的邪恶计划—这是一个假设。你不想说任何话语来引导杀人犯找到你的朋友,可是问题在于,你会说什么呢?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直接撒个谎:“不,她不在这里。”或者你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然而却具有误导性的陈述:“一个小时之前,我在路那头的杂货店里看见过她。”
从康德的角度来说,第二种策略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第一种则不是。你可能认为这有点吹毛求疵。从道德上来说,一个策略性的、真实而具有误导性的表达与一个直率的谎言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两种情形中,你都是在希望能够误导杀人犯相信,你的朋友并没有藏在房子里。
康德相信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善意的谎言”—那些我们有时候出于礼貌、避免伤害感情而说的一些无伤大雅的假话。假设一个朋友送给你一件礼物,你打开盒子,看见了一条极其难看的、你一辈子都不会系的领带。你会说什么呢?你可能会说:“真漂亮!”这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或者你会说:“你真是太客气了!”或者“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带!谢谢你!”这些话就像善良的谎言,会给你的朋友这样一个错觉,即你喜欢这条领带。可是它们都不是真实的。
康德可能会反对善意的谎言,因为这就基于结果主义的理由而使得道德法则有了例外。体谅他人的感情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目的,可是我们必须以一种与绝对命令相符合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目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愿意将自己赖以行动的原则普遍化。如果每当我们认为自己的目的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就能够破例,那么道德法则的绝对性特征就被破坏了。与之相反,真实而具有误导性的表达,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威胁到绝对命令。事实上,康德自己在面临一个困境时,就曾利用过这一区别。
在与贡斯当展开争论的前几年,康德发现自己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之间有些麻烦。国王及其检察官认为康德关于宗教的著作贬低了基督教,并要求他答应不再就此话题发表任何意见。康德以一段措辞谨慎的陈述作了回应:“作为陛下忠实的臣民,我将彻底停止所有与宗教有关的公共演讲和论文写作。” [193]
当康德做出这一陈述时,他知道这位国王不会活太久了。在国王驾崩几年之后,康德认为自己从这一承诺中解脱开了,因为该承诺仅仅对“作为陛下忠实的臣民”的他而有所束缚。康德后来解释道,他在挑选这些措辞时“非常仔细,以至于我不会被永远地剥夺权利……而仅仅只是当陛下活着的时候”。 [194] 借助于这一聪明的措辞,普鲁士的这位道德典范,成功地误导了检察官们而没有对他们撒谎。
有些吹毛求疵?可能是的。不过,在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与一个精明的伎俩之间,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近些年来人们的印象当中,没有哪个美国公众人物能够比他更加谨慎地措辞,或巧妙地为自己辩护。在他第一任总统竞选期间,当被问及他是否曾经使用过软性毒品时,他回答道: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他们那个地区或州的反毒品法。后来,他承认在英国牛津大学上学时,曾经尝试过大麻。
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否认,来自于他对相关报道说他在白宫里与22岁的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发生性关系的回应:“我想对美国人民说一件事,我希望你们听我说……我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后来人们发现,总统确实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过性关系,并且这一丑闻引起了一次弹劾诉讼。在弹劾听证会上,一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与克林顿的律师格雷戈里·克雷格,就总统关于“性关系”的否认是不是一个谎言而进行了争论:
鲍勃·英格利斯 :那么,克雷格先生,当他说“我从来没有与那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时,他是否对美国人民撒谎了?他是否撒谎了?
克雷格 :他确实误导并且欺骗了……
英格利斯 :稍等一下,他是否撒谎了?
克雷格 :对美国人民来说—他误导了他们,并且当时没有告诉他们真相。
英格利斯 :好吧,看来你并不准备回答—而且总统本人也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法律性的、技术性的东西来遮蔽这一简单的道德事实。当他说“我从来没有与那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时,他是否对美国人民撒谎了?
克雷格 :他并不认为自己撒谎了,并且由于那种方式—让我来解释这一点……解释一下,议员先生。
英格利斯 :他认为自己没有撒谎?
克雷格 :是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撒谎了。因为他关于“性关系是什么”的概念是字典上所给出的定义。实际上,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可是在他自己的观念中,他的定义并不是……
英格利斯 :好吧,我明白这个论证了。
克雷格 :好的。
英格利斯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现在坐在我们面前,并收回他所有的—他所有的道歉。
克雷格 :不是的。
英格利斯 :你在收回这些道歉,不是吗?
克雷格 :不,我没有。
英格利斯 :因为你现在回到了这一论证—你在这里可以做出很多论证。其中之一就是:他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那只是口交,而并不是真正的性行为。那么,这是否是你今天在这里要对我们说的:他并没有与莱温斯基发生性行为?
克雷格 :他对美国人民所说的是:他并没有发生性关系。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一点,议员先生,因为这—你可能将这看做一种技术性的辩护或一种钻牛角尖的、闪烁其词的回答。然而,任何一部字典都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对性关系加以定义的;但是他并没有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那种性接触……因此,他欺骗了美国人民吗?是的。这是不对的吗?是的。这值得谴责吗?是的。 [195]
总统的律师承认,也正如克林顿所承认的,他与这名实习生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适当的,也是值得谴责的,并且总统关于这件事的发言“误导并欺骗了”公众。他唯一拒绝承认的是,总统撒谎了。
那么,在这种拒绝中,是什么受到了威胁呢?对此的解释不可能仅仅是法律性的,即在誓言下、法庭证词中或法庭上撒谎,是指控其作伪证的依据。这件事中的发言并不是在宣誓中做出的,而是面对美国公众的一次电视发言。而这位共和党的检察官和克林顿的辩护人都认为,在确认克林顿是在撒谎还是仅仅在误导和欺骗时,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受到了威胁。在他们关于“撒谎”这个词—他是否撒谎了—的言辞激烈的对话当中,佐证了一种康德式的思想:在谎言与误导性的实话之间,有着一种与道德相关的差别。
可是,这种差别会是什么呢?这两种情况中的意图可以说是一样的。我是对门口的杀人犯撒谎,还是给他提供一种机智的措辞,我的意图都是为了误导他认为我的朋友并没有藏在我的房子里。并且,根据康德的道德理论,重要的正是意图或动机。
我认为这里的差别在于:一种精心设计的措辞,以某种方式对说实话的这一义务心存敬意,而一个直率的谎言则并不如此。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厌其烦地编造一种具有误导性但在技术上却是真实的陈述—而一个简单的谎言也可以同样表达,那么,无论他是多么闪烁其词,他都是尊重道德法则的。
一种误导性的真话包括两个动机,而不是一个。如果我仅仅对杀人犯撒谎,我是出于一种动机而这样做—为了保护我的朋友不受伤害。如果我告诉杀人犯,我最近在杂货店看到我的朋友了,我是出于两种动机而这样做—保护我的朋友,同时维护说实话的义务。在这两种情形当中,我是在追求同一种令人称赞的目的,即保护我的朋友。而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中,我是以一种与义务的动机相一致的方式去追求这一目的的。
有些人可能反驳道,与谎言一样,一种技术上真实却具有误导性的陈述,不可能毫无矛盾地被普遍化。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一差别:如果每个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站在门口的杀人犯,或一种令人尴尬的丑闻时都撒谎,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陈述,因此这些陈述就不会起作用。但误导性的事实陈述却不会如此。如果每个人发现自己身处危险的或尴尬的处境时,都寻求一种措辞谨慎的推托,那么人们并不必然会不再相信它们,而会学着像律师那样去听,并且在考虑到这些陈述字面上的意思的同时,从语法上加以分析。这也正是当媒体和公众熟悉了克林顿措辞谨慎的否认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康德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事态—人们从语法上分析政客们的否认所具有的字面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没有人相信政客们的那种情况要好一些。这是一种结果主义的论点。康德的意思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然而却是真实的陈述,并没有以那种与直率的谎言同样的方式强迫或操纵了听众。一个谨慎的听众总是有可能把它弄明白。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根据康德的道德理论,针对门口的杀人犯、普鲁士的检察官,或某个特别检察官的那些真实但却具有误导性的陈述,以某种方式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而那种赤裸裸的谎言则并非如此。你们可能认为,我至今为止论证得太费力了,却不能将康德从一种不合情理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康德的主张—对门口的杀人犯撒谎是不对的—可能在根本上是无法辩护的。然而,一个率直的谎言和一个误导性的实话之间的差别,有助于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它还显示出比尔·克林顿和哥尼斯堡这位严肃的道德哲学家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与亚里士多德、边沁及密尔有所不同,康德在政治理论方面并没有巨著,而只有一些论文。然而,源于其伦理学著作中的那些对于道德和自由的论点,却有着强有力的关于公正的含意。尽管康德并没有详尽地论证这些含意,但是他所支持的政治理论反对功利主义,而支持一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
首先,康德不仅反对功利主义作为个体道德的基础,也反对它作为一项法律的基础。他认为一种公正的宪法应当力图使不同个体的自由能够相融合。它与功利最大化没有关系,后者“绝不能干涉”基本权利的规定。由于人们“在幸福的经验性目的及其构成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功利不能作为公正和权利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将权利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那么,就会要求这个社会来肯定或接受某一种幸福观而不接受另外一些;将整个宪法都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幸福观(如大多数人的幸福观)之上,就会给其他人强加一些价值观,这就没有尊重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目的的权利。“没有人能够强迫我的幸福必须与他那种关于他人福利的观念相一致,”康德写道,“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只要他不侵犯他人也这样做的自由。” [196]
康德的政治理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从社会契约—但却是一个带有令人困惑的偏执的社会契约—中得出公正与权利。早些时候的契约论思想家们,包括洛克,都认为合法政府源于人们在某个时刻、基于那些即将支配他们集体生活的各种原则,而自行订立的一种社会契约。可是康德并不这样看待契约。尽管合法政府必须基于一种原初的契约,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认为这一契约……作为一个事实而真实地存在,因为它不可能是这样的”。康德坚持认为,原初性的契约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出于想象。 [197]
为什么要从一种假想的契约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得出一部公正的宪法呢?第一个原因是实际性的:我们经常难以证明,在各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真的产生过社会契约。第二个原因是哲学上的:道德原则不能仅仅来源于经验性的事实。正如道德法则不能建立在个体的利益或欲望基础之上一样,公正原则也不能建立在一个共同体的各种利益和欲望基础之上。“过去有一群人通过了一部宪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足以使得该宪法就是公正的。
那么,什么样的假想的契约可能避免这一问题呢?康德简单地称之为“一种理性的观念,但它却具有确定无疑的实践性的现实性;因为它能够要求每一个立法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其法律—使这些法律可能产生于整个民族的集体意志”,并使每个公民都负有义务,“就好像他已经同意了”。康德总结说,这种假想的集体同意的行为“是任何一项公共法律的公正性的试金石”。 [198]
康德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假想的契约可能会是什么样,或者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公正原则。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从未签署过社会契约。事实上,美国那些实际上同意遵守宪法的人(公共官员们除外),只有那些自然公民—那些移民,宣誓忠诚于宪法,以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表示同意。因此,我们为什么有义务服从于法律呢?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我们的政府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的呢?
约翰·洛克(John Locke)说,我们已经给出了心照不宣的同意。任何一个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即使只是在高速公路上穿行,也含蓄地对其法律表示同意,并受其约束。 [200] 然而,心照不宣的同意,是实际事物的一种苍白无力的形式。我们很难明白,仅仅穿过一个城镇如何就在道德上类似于认可宪法。
伊曼纽尔·康德诉求于假想的同意。一项法律如果能够得到全体公众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公正的。然而,这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对真实社会契约的代替。一个假想的合约,如何能起到一个真实契约的道德作用呢?
约翰·罗尔斯(1921~2002)是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答案。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当中,他主张,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要询问,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我们会认可什么样的原则。 [201]
罗尔斯的推理如下:假设我们当时聚集到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来选择一些管理我们集体生活的原则,也即,起草一份社会契约。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人会支持不同的原则,这体现出他们各种各样的利益、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地位等。有些人很富,而有些人很穷;有些人拥有权力并社交广泛,而有些人则并非如此;有些人属于少数种族、民族或宗教,而有些人则不是。我们可能会达成一种妥协,然而即使是这种妥协,也很可能反映出某些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要高于另外一些人。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社会契约会是一种公正的安排。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种思想性的实验:假设我们聚集在一起来选择各种原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将身处何处。假设我们在一道“无知之幕”的背后进行选择,这道“无知之幕”将暂时不让我们知道任何关于我们自己是谁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阶层或性别、种族或民族、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我们是健康还是体弱多病,是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中学辍学,是出生于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还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实际上就会从一种原初的平等状态而进行选择。因为没有人会有一个更高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那么我们所同意的各种原则就会是公正的。
这就是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念—一种假想的、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所达成的协议。罗尔斯要求我们询问:我们—作为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他没有假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而只是假设我们为了这个思想实验而搁置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呢?
首先,他推理说,我们不会选择功利主义。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想:“据我所知,我可能会是一个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成员。”没有人愿意冒险甘做那个被扔给狮子以娱乐大众的基督徒,也没有人会选择一种纯粹的政府放任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后者将赋予人们一种权利以保留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赚来的所有钱财。“我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每个人都会这样推理,“可是,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我要避免一种可能让我一无所有,却得不到帮助的体制。”
罗尔斯认为,从这种假想的契约中,会产生两种公正原则。第一个原则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一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第二个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尽管它并不要求一种平等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它却只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哲学家们争论,罗尔斯假想的社会契约中的各派,是否会像他所说的那样选择这些原则。稍后我们将看到,为什么罗尔斯认为人们会选择这两个原则。然而,在讨论这些原则之前,让我们先讨论一个在此之前的问题:罗尔斯的思想性实验是思考公正的正当方式吗?公正原则如何能够产生于一种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的协议之中?
要想理解罗尔斯假想契约的道德力量,有必要先了解实际契约所具有的道德局限。我们有时候会假设,当两个人做一项交易的时候,他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一定是公平的。换言之,我们假设,合同会使那些产生于它们的各种条款正当化。然而,它们并不如此—至少它们自己不能。实际的合同并非自足的道德工具。你和我做交易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使这项交易就是公平的。人们总是能够对任何一个实际的合同提出质疑:“它是公平的吗?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指向协议本身,我们需要一些与公平有关的独立的标准。
这一标准可能从哪里得出呢?可能你会想,它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在此之前的合同—如一部宪法。可是,宪法也容易受到像其他协议一样的质疑。宪法是由人们认可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其条款就是公正的。让我们来考虑一下1787年的美国宪法:尽管它有着诸多优点,可是它却由于认可奴隶制而被玷污了,这一瑕疵一直保留到内战以后。宪法被费城的代表所认可以及后来被国家所认可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使它就是公正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瑕疵可以追溯到同意的不足。作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并没有被包括在立宪会议当中,妇女也没有,后者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才赢得了选举权。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当然很可能产生一部更加公正的宪法;可是,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没有哪一种社会契约或立宪会议—无论多么具有代表性—能够保证会产生出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
对于那些认为道德始于同意、也结束于同意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刺耳的主张。然而,这并不那么容易引起争议。我们经常质疑人们所做的那些交易的公平性,我们也熟悉能够导致不良交易的那些偶然性:交易的一方可能是个更好的谈判者,或者有着更好的交易地位,或者对所交换物品的价值了解得更多。唐·科里昂(Don Corleone)在《教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我将给出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价格。”这(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那种体现于大多数谈判中的压力。
认识到这些合同并不赋予它们所产生的那些条款以公平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高兴的时候就违反这些协议。我们可能有责任履行一个甚至是不公平的交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同意很重要,即使对公正而言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然而,它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我们经常将同意的道德作用与其他义务之源混淆在一起。
假如我们做一项交易:你给我100只龙虾,我付给你1 000美元。你大获丰收并运来了龙虾,我大快朵颐之后却拒绝付钱。你说我欠你这笔钱。“为什么呢?”我问道。你可能会诉诸我们的协议,也可能会诉诸我所享受的利益。你可能会很好地说明,我有义务偿还我所享受的那些由你而来的利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做了同样的一笔交易,不过这一次,在你捕获到龙虾并将它们运到我门前的时候,我改变主意了。我根本就不想要它们。你仍然想收钱,而我说:“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一次我并没有获利。”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诉诸我们的合同,不过,你也可能会诉诸你捕获龙虾所做的辛苦工作,并指望我会购买它们。你可能会说,我有义务支付那由于我而让你所付出的努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否想象一个义务仅仅基于同意的情形,也即没有偿还某利益,或补偿你为我所做的工作而增加的道德力度。这一次,我们做了同样的交易,然而,过了一会儿,在你还没有花费时间捕捉龙虾之前,我打电话给你:“我改主意了,不想要龙虾了。”那么我是否仍然欠你1 000美元呢?你是否会说“交易就是交易”,并坚持认为,“我同意”这一行为本身就已产生了一种义务,即使没有任何利益或依据?
法律思想家们关于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同意本身能够产生一种义务吗,还是也需要某种利益或依赖的因素? [202] 这一争论告诉了我们一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与合同道德相关的信息:只要实际的合同实现了两种理想—意志自由和互惠,那么它们就具有道德分量。
作为自愿的行为,合同体现出我们的意志自由;它们所产生的义务之所以具有分量,是因为它们是自我给定的—我们自由地、自主地承担它们。作为相互谋取利益的手段,合同利用了互惠性的理想;履行这些合同的义务,产生于那种偿还他人给我们提供的利益的义务。
实际上,这些理想—意志自由和互惠性—都没有完全实现。有些协议尽管是自愿的,却不是相互获利的;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仅基于互惠而有义务偿还一种利益,甚至都不需要合同。这便指出了同意的道德局限性:在某些情形中,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不需要同意。
让我们来考虑两种体现出同意本身并不够的情形:在我的两个儿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收集棒球卡并且相互交换。大儿子对那些棒球球员以及卡片的价值了解得更多,他经常向弟弟提出一些不公平的交易—比如,用两张能打各种位置的内野手 (8) 来换小肯·格里菲(Ken Griffey,Jr.)。因此我订立了一条规定:只有经过我同意,才能完成交易。你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家长式的专制,确实如此。(这就是家长式专制的目的。)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中,自愿的交换显然是不公平的。
几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这一案例更为极端:芝加哥一名年迈的寡妇,她的公寓里的马桶漏水了,于是她雇用了一名承包商来修理,费用为5万美元。她签署了一份分期付款的合同,首付2.5万美元。当她去银行提取2.5万美元的时候,这一阴谋被揭穿了。银行出纳员问老妇为什么取这么一大笔钱,她回答说需要付钱给水管工。出纳员联系了警方,警方以欺诈的罪名逮捕了那个无耻的承包商。 [203]
除了那些最热忱的契约至上主义者们,所有人都会认为5万美元的马桶修理费异乎寻常地不公平—尽管在事实上,相互同意的双方认可这一价格。这一事例说明了合同所具有的两点道德局限:首先,一项协议的事实,并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其次,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主张。这种合同并不能作为相互获利的手段,因为它并不尊重互惠的理念。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人会说,老妇在道德上应当支付那笔骇人听闻的费用。
可能有人回应说,修理马桶的这一欺诈并不是一份真正自愿的合同,而是一种剥削,其中一个无耻的水管工欺骗了一个一无所知的老妇。我对这个案件的具体细节并不知情,不过为了论证我们可以假设,水管工并没有强迫老妇,并且她在认可这一交易时头脑非常清醒(尽管她对于水管装修工作的报酬知之甚少)。该协议是自愿的这一事实,绝不能保证它就包含了平等的交换或利益的对称。
到目前为止,我论证了同意并不是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一项不平衡的交易可能远没有达到相互获利,以至于其自愿性特征也不能使它免受责难。现在我想提出一种更进一步的、更具挑衅性的主张:同意也不是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如果相互间的获利足够明确,那么,即使没有同意的行为,互惠性的道德主张也可能站得住脚。
浮现于我脑海中的这种事例,是18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遇到过的。休谟在年轻的时候,曾针对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写过一篇尖锐的批评。他称之为“哲学上的虚构,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现实性”, [204] 以及“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神秘、最无法理解的运作之一”。 [205] 多年之后,休谟有了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检验了他反对将同意作为义务基础的立场。 [206]
休谟在爱丁堡拥有一座房子,他将它租给了他的朋友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后者又将房子租给了一个转租人。该转租人认为这座房子需要作一些维修,于是他就雇用了一名承包商来做此工作,而没有征求休谟的意见。该承包商作完维修后将账单送至休谟面前。休谟拒绝付账,理由是他并没有同意作维修,也没有雇用这名承包商。这一事件后来交由法庭裁决。该承包商承认,虽然休谟并没有同意,可是房子需要维修,并且他做了这些维修工作。
休谟认为这是一个欠妥的论证。他告诉法庭,该承包商的主张仅仅是“这项工作有必要去做”。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基于同样的规则,他可以进入爱丁堡的任何一座房子,做一些他认为适合做的事情,而无须事先征得房主的同意……并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出同样的理由:这项工作是必要的,而且之后房子更好了”。可是,休谟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很新的理论……可是完全站不住脚”。 [207]
在谈到这一房屋维修事件时,休谟就不喜欢一种纯粹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理论了。但是他的辩护失败了,法庭判定由他付这笔钱。
“偿还一种利益的义务,可以不需要同意就能产生”,这一思想在休谟的房子这一事例当中,貌似具有道德合理性。然而,这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溜进强硬的销售策略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橡皮清洁工”成为纽约街头一道令人生畏的风景。他们配有一把橡皮清洁刷和一桶水,会突然出现在一辆停在红灯前的汽车面前,然后开始清洗挡风玻璃(经常不问驾驶员是否允许)并索要费用。他们正是基于休谟的承包商所援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理论而进行运作的。然而,如果没有同意的话,执行一项服务与行乞之间的界限就会经常变得很模糊。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决定全力打击这些橡皮清洁工,并命令警察逮捕他们。 [208]
当以同意为基础的义务,与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时,就会出现以下这一容易引起混淆的事例。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我与一帮朋友驾车周游全国。我们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走进一家便利店。当我们回到车上时,却发现车子发动不了了。我们当中没有人懂得修理汽车。当我们正在考虑怎么办的时候,一辆厢式货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车身上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萨姆汽车维修”。从车里下来一个男人,大概就是萨姆。
他走到我们跟前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是这样工作的,”他解释道,“我每小时收50美元。如果我在5分钟之内修好你们的车,你们得付我50美元;如果我工作1个小时却还是修不好,你们也得付我50美元。”
“你能修好的概率有多大呢?”我问道。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在汽车转向柱底下捣鼓。我当时不确定该做什么,于是看着朋友们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片刻之后,这个人从转向柱底下钻了出来,说道:“点火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还有45分钟,想让我去汽车发动机罩底下看看吗?”
“等一等,”我说道,“我还没有雇用你呢。我们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个人非常生气,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刚才我在转向柱底下查看的时候,修好了你的车,你也不会付钱给我?”
我说:“不是一回事儿。”
我并没有讨论以同意为基础的义务与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之间的区别,我也不认为这会有什么帮助。但是,与修理工萨姆之间发生的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倒是体现了一种常见的、与同意有关的困惑。萨姆认为,如果他在捣鼓转向柱的时候修好了我们的车,那么我就得付他50美元。我对此表示同意。可是,我之所以付他这笔钱的原因在于,他提供了一项帮助,即修好了我的车。他推断,由于我得付他钱,所以我就肯定(暗含的)同意雇用他。但是这一推论是个错误,它错误地假设,有义务的地方就肯定有协议—某种同意的行为。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没有同意,义务也有可能产生。如果萨姆修好了我的车,那么我将出于互惠性的名义而付他钱;如果仅仅是谢谢他便驾车而去,会不太公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雇用了他。
当我给学生们讲这个故事时,他们大多数都同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并不欠萨姆50美元。可是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学生的理由与我的并不相同。他们认为,由于我并没有明确地雇用他,所以我并不欠他任何东西—即使他修好了我的车,我也不欠他钱。任何报酬都将只是一种出于慷慨的行为—是一种感激,而非义务。因此,他们为我辩护,并不是由于接受了我的广泛义务观,而是由于他们坚持一种苛刻的同意观。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道德主张都包含了同意,然而,如果我们不承认互惠的独自分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生活。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婚姻的契约。假设我这一方在忠诚于婚姻20年之后,发现我的妻子一直在与另外一个男人约会,那么我可能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而在道德上感到愤怒。第一种诉诸同意:“我们有一个约定,你发过誓,你违背了承诺。”第二种则诉诸互惠性:“我这一方一直如此忠诚,我当然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这不是回报我的忠诚的方式。”如此等等。第二种抱怨并没有涉及同意,它也不需要同意。它在道德上似乎是合理的,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交换结婚誓言,而是作为伴侣生活了这么多年。
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告诉了我们与契约道德相关的什么内容呢?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然而,大多数实际的契约都缺乏这些理念。如果我与某个具有更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人打交道的话,我的同意可能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或者在极端情形下,是被强迫的。如果我与某个对我们所交换之物更为了解的人谈判,那么这一交易可能就不是相互获利的;在极端情形下,我可能是被欺诈或蒙骗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处境大不相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交易力量和知识总是可能的。而只要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协议的既成事实本身,就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中的契约并不是自足的道德工具,我们总是能合情合理地质疑:“他们所达成的协议是否公平呢?”
让我们来想象一种在那些拥有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权力和知识的人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他们处于同样的境况,而并非不同的境况。同时也设想一下,这份契约的对象并不是管道铺设或其他普通的交易,而是那些治理我们的生活的、分配我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各种原则。在这样的各方中所达成的这样一个契约,就不会有压迫、欺骗或其他不公平的缺点。它的各项条款由于同意本身,就必然是公正的,而无论它们是什么。
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契约,那么你就理解了罗尔斯的这一观念:平等的原初状态中的假想契约。无知之幕保证了原初状态所需要的权利和知识上的平等。无知之幕通过保证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优点或缺点、他的价值或目的,从而保证了没有人能够(即使是无意地)利用一种更好的交易地位。
如果允许有特殊知识,那么结果就由于任意的偶然性而有所偏袒……如果原始状态是为了产生公正的契约,那么,契约各方就必须处于平等的境况,并被当做有道德的人而同等地对待。必须通过调节最初契约状态的环境,而纠正这个社会的任意性。 [20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假想契约,并不是现实契约的一种苍白无力的形式,因而在道德上比较虚弱;它是现实契约的纯粹形式,因而在道德上更有力量。
假设罗尔斯是正确的: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询问,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的平等状态中,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原则呢?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我们不会选择功利主义。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得到郑重的对待。如果我们最终在社会中是一个少数民族或小宗教团体的成员,我们不希望被压迫,即使这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快乐;一旦无知之幕被揭开,而开始了真实生活,那么我们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宗教压迫或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为了预防这些危险,我们就要反对功利主义,并同意一种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平等自由的原则,包括意识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并且我们会坚持认为,这一原则,要优先于那些使总体福利最大化的各种尝试;我们就不会为了社会和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根本性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来治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呢?为了避免我们自己身处极度贫困的危险,我们可能一开始会想着要支持一种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政策。然而,我们可能接着会想到,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是为了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假设我们通过允许某些不平等,如给医生所支付的工资要高于汽车驾驶员的工资,可以改善最不利者的境况—如为穷人增加医疗机会。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可能接受罗尔斯所说的“差异原则”: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利益时,它们才是可允许的。
那么这种差异原则到底有多少平等主义的意味呢?这很难说,因为工资差异的效用,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让我们假设,给医生更高的报酬,能够给贫困的边远地区带来更多更好的医疗保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工资的差异就可能与罗尔斯的原则相一致。然而,假如给医生更高的报酬,对于阿帕拉契山区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影响,而仅仅是给贝弗利山庄带来了更多的整容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种工资的差异就很难得到辩护。
那么,迈克尔·乔丹的丰厚收入与比尔·盖茨的巨额财富又如何呢?这些不平等与差异原则能够一致吗?当然,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是要评价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工资的公平性,它所关心的是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权利与义务、收入与财富、权力与机会的分配方式。对于罗尔斯而言,他所要询问的是:作为部分体制的结果,盖茨的财富从整体上来看,是否有利于那些社会最不利者。例如,它是否服从于一种激进的、向富人征税来给穷人提供医疗、教育及福利的税务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且如果这一体制使得穷人比他们在一个更加严格的平等安排中的状况要更好的话,那么这种不平等就能够与差异原则相一致。
有些人质疑,处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不会选择差异原则。罗尔斯怎么知道,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人们不会赌一把,愿意选择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以期处于社会顶层呢?可能有些人甚至会愿意冒险沦为毫无土地的农奴以寄希望于成为一位国王,而由此选择一种封建制度社会。
罗尔斯认为人们在选择那些支配自己根本性的生活前景的原则时,并不会冒这样的险。除非他们知道自己热爱冒险(而这又是一种被无知之幕所屏蔽的特质),人们不会下高风险的赌注。可是罗尔斯支持差异原则的理由,并不完全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在原初状态中会反对冒险。在无知之幕这一设置的背后是一种道德论证,后者可以独立于思想性的实验而得到体现;其主要思想是:关于收入和机会的分配,不应当依赖于那些从道德上来说具有任意性的因素。
罗尔斯从封建特权统治开始,比较了多种不同的公正理论,从而提出这一论点。现在,没有人维护封建特权统治或种姓制度的公正性。罗尔斯论述道,这些体制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根据出生的偶然性来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权力。如果你出身于贵族家庭,那么你就拥有各种从那些生而为奴的人们那里剥夺而来的权利和权力。可是,你所出生的环境并不是你的行为结果。因此,基于这些任意性的因素而设定你的生活前景,是不公平的。
市场社会纠正了这些任意性,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将就业机会对具有所需要的才能的那些人开放,并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保证公民们能够得到平等的基本自由,并且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由自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一体制—一个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正理论相契合。相对于封建制和种姓等级制社会而言,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它反对一成不变的出生等级制度。它允许每个人都合法地奋斗与竞争。
那些拥有良好家庭背景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那些没有这些的人们,具有明显的优势。允许每个人都进入比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如果选手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那么比赛就很难说是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认为,那源于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自由市场的有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能看做公正的。自由至上主义体制的最明显的不公正,在于“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在道德上看来非常任意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210]
纠正这种不公平的途径之一,就是纠正社会和经济的不足之处,一种公平的精英统治制度(meritocracy)试图通过超越单纯的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做到这一点。它通过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使得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人们,能够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与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相竞争—而除去了通往成功之路的诸多障碍。它着手实行一些启智计划(Head Start Program)、儿童营养与医疗计划、教育与工作培训计划等任何将每个人—无论阶层或家庭背景—放置在同一起点上所需要的东西。这种精英统治制度的观念认为,源于一个自由市场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但是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来发展他的各种能力的时候。只有当每个人都开始于同一个起跑线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应当得到奖励。
罗尔斯认为,这种精英统治的观念纠正了某些道德上的任意性的优势,但却仍然达不到公正。因为,即使你设法将每个人带到同一起跑线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或多或少地预测谁将赢得这一比赛—那些跑得最快的选手。然而,作为一个跑得快的选手,并不完全是我的行为结果,这在道德上具有偶然性,就像我来自于一个富裕家庭是偶然的一样。“即使它能够完美地消除社会偶然性的影响”,罗尔斯写道,这种精英统治制度“仍然允许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由各种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所决定”。 [211]
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教育机会的社会中运转的自由市场,也不能产生一种公正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其原因在于:“分配的份额受制于自然运气的产物,而这种产物从道德上来看具有任意性。我们没有理由允许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要受到自然资产的分配来确定,就像我们没有理由允许它受历史和社会运气的确定一样。” [212]
罗尔斯总结道,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观念是有缺陷的,其理由与自由至上主义的观念一样(尽管在程度上要稍稍轻微一些):它们都将分配的份额建立在那些具有道德任意性的基础之上。“一旦我们在决定分配份额时,要么受到社会偶然性影响的困扰,要么受到自然机会影响的困扰,那么经再三考虑,我们就注定要受到一种影响的困扰。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两者似乎具有同等的任意性。” [213]
罗尔斯认为,一旦我们注意到,自由至上主义和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理论都体现出道德任意性,那么,如果缺乏一种更加平等的观念,我们就不能满足。然而,这一观念可能是什么呢?纠正不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一回事,而纠正不平等的天赋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受到这一事实(有些选手比另一些选手跑得更快)的困扰,那么,我们就得让那些具有天赋的选手穿上铅制的鞋子吗?一些平等主义的批评者们认为,精英统治的市场社会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种均等,后者给那些有天赋的人强加了一些困难。
《哈里森·伯杰龙》(Harrison Bergeron)是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Jr.)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它作为一种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表达了以上的那种担忧。小说是这样开头的:“那是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没有哪个人比别人聪明些,没有哪个人比别人漂亮些,也没有哪个人比别人强壮些或者灵巧些。”这种绝对平等由美国仲裁将军手下的工作人员执行。那些超过正常智商水平的公民,需要在耳内戴上一个微型智能障碍收音机,每隔20秒钟,一个政府发射台就会发送一种尖锐的噪声以阻止他们“不公平地利用他们的大脑”。 [214]
哈里森·伯杰龙年仅14岁,他异乎寻常地聪明、英俊并拥有天赋,因此他不得不装配比大多数人更重的障碍。与那种微型耳塞式收音机不同,“他戴着一副巨大的耳机和厚得像酒瓶底似的眼镜”。为了掩盖他那英俊的外表,哈里森被要求“在鼻子上戴一个红色的橡皮球,刮掉眉毛,洁白整齐的牙齿上套着胡乱造出的黑色暴牙套子”。此外,为了抵消他强壮的身体优势,他不得不在走动时戴着沉重的破铜烂铁。“在人生的这条赛道上,哈里森负重300磅。” [215]
一天,哈里森脱去了他的障碍物,以此作为英勇地反抗平等主义专制的行为。我不打算透露这个故事的结尾而毁了它。我们应该已经很清楚,冯内古特的小说是如何对平等主义的公正理论,提出了一种生动而熟悉的抱怨。
然而,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却并不容易受到这种反驳的攻击。他表明:一种绝对的平等,并不是精英统治的市场社会的唯一备选项。罗尔斯的备选项—他称之为差异原则—能纠正那种关于才能和天赋的不公平分配,而同时又不给那些有天赋的人设置障碍。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鼓励那些有天赋的人发展并锻炼自己的才能,不过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才能在市场中所获得的回报属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我们不要给那些跑得最快的人设置障碍,让他们去跑并做到最好;但是要事先认识到,这些奖品并不只属于他们,而应当与那些缺乏这类天赋的人们共同分享。
尽管差异原则并不需要一种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但是其潜在性的观念却表达出一种强有力的,甚至是激励人心的关于平等的洞见:
差异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协议,即将自然才能的分配看做一种公共资产,并共享这一分配的好处,而无论其结果是什么。那些受到自然宠爱的人们,无论他们是谁,都只有当他们的好运气改善了那些不利者的状况时,才能从自己的好运气中获利。那些在天赋上占优势的人们,不能因为天分较高而仅仅自己受益,而要通过抵消那些训练和教育所产生的费用,从而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们。没有人应当得到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没有人在社会上值得拥有更加有利的起点。然而这并不由此产生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应当消除这些差别。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处理它们。人们能够安排社会的基本结构,以至于这些偶然性对那些最不幸者有利。 [216]
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四种不同的分配公正理论:
1. 封建制度或种姓制度:基于出生的固定等级制
2. 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3. 精英统治制度:拥有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4. 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罗尔斯认为,前三种理论将分配份额建立在那些从道德上看来具有任意性的因素之上—要么是出生的偶然性,要么是社会和经济的优势,要么是自然才能和能力等。只有差异原则避免了将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建立在这些偶然性基础之上。
尽管这种源于道德任意性的论点,并不依赖于那种源于原初状态的论点,但是它们在以下方面是相似的:两者都坚持认为,我们在考虑公正时,应当抽象于或悬置那些关于人们及其社会地位的偶然性事实。
罗尔斯支持差异原则的理由,引发了两种主要的反驳:首先,激励会如何呢?如果那些有才能的人,只有在有利于最不利者时才能获利,那么,如果他们决定更少地工作,或在一开始就不发展他们的技能,那会怎么样?如果税率很高或报酬差异很小,难道那些有天赋的、很可能已经成为外科医生的人,不会进入那些要求较低的工作行列吗?难道迈克尔·乔丹不会更少地训练跳起投篮,或更早地退休吗?
罗尔斯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我们需要这些刺激来帮助诸多最不利者,那么,差异原则允许为了激励而在收入上有所不同。仅仅给那些首席执行官支付更高的工资或给富人减税,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做法是不够的。不过,如果这些激励能够产生出经济上的增长,而这种经济上的增长使得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的状况,要比他们生活于一个更加平等的制度安排中的状况更好,那么差异原则就会允许这些激励的存在。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允许为了激励而在工资上有所差异,并不等于是说,那些成功人士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享有一种特殊的道德所有权。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当收入的不平等,能够产生那些最终能够帮助最不利者的成果时,它才是正当的,而不是因为那些首席执行官或体育明星应当比工厂工人赚更多的钱。
这就将我们引领至那种针对罗尔斯公正理论的第二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反驳:努力又会怎样呢?罗尔斯反对精英统治制度的公正理论,理由是:人们的自然才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可是,人们培养自己的才能所付出的那些艰辛的努力又如何呢?比尔·盖茨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而创立发展了微软;迈克尔·乔丹在训练其篮球技能上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其数。尽管他们拥有才能和天赋,但是,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奖励吗?
罗尔斯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种有利的、培养的产物。“即使那种愿意去努力、去尝试以及成为应得的意愿本身,在其一般意义上来说,也取决于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217] 与其他的成功因素一样,努力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后者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获得的。“有一点似乎很明显:一个人所心甘情愿付出的努力,要受到他的自然能力和技能以及对他所开放的机会的影响。那些拥有更多天赋的人,如果其他方面等同的话,他们更可能尽心尽力地去奋斗……” [218]
当我的学生们在面对罗尔斯关于努力的论点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就,包括进入哈佛,所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那些超越于他们掌控的、具有道德任意性的因素。许多同学带有疑虑地看待任何一种这样的公正理论,即那种认为我们在道德上并不应得那些凭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的公正理论。
在我们讨论了罗尔斯关于努力的主张之后,我作了一项不科学的调查。我指出:心理学家们认为,出生顺序会影响努力和奋斗—如学生们所认为的、与进入哈佛相关联的努力。据报道,在家里第一个出生的人,要比他的弟弟妹妹们具有更强的职业道德,挣更多的钱并获得更普遍的成功。这些研究具有争议性,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否真实。然而,也就是随便玩玩,我问学生们有多少人在家里是第一个出生的。大约有75%~80%的同学举手了,这一结果跟我每一次作这个测验所获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没有人会认为,第一个出生是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如果像出生顺序这样的具有道德偶然性的事物,能够影响我们努力工作和认真奋斗的倾向,那么罗尔斯可能是有道理的,即使努力也不能作为道德应得的基础。
这一主张—人们应得到由于努力和艰辛工作而获得的回报—还由于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而值得怀疑:尽管精英统治制度的支持者们经常援引努力的美德,但是他们并不真的认为,努力应当单独地成为收入和财富的基础。让我们来设想两个建筑工人,一个强壮结实,能够毫不费力地一天筑四堵墙;另一个则瘦弱无力,一次都不能搬动两块砖。尽管后者工作非常努力,可是他要耗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他那个强壮的同事不太费力一天就能做完的事情。没有哪一个精英统治制度的维护者会说,这个瘦弱但工作努力的工人应当得到更多的工资,因为他比那个健壮的人所付出的努力更多。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迈克尔·乔丹。他确实训练得非常刻苦,可是有些不太出名的篮球运动员甚至训练得更加刻苦。没有人会说,他们应得一份比乔丹更丰厚的合同,以作为对他们所付出时间的一种奖励。因此,尽管精英统治者们谈论到了努力,可是他们却相信,其实是贡献或成就才值得奖励。无论我们的职业道德是不是自己的行为结果,我们的成就,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都取决于那些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地拥有的各种自然才能。
如果罗尔斯关于才能的道德任意性的论点是对的,那么,这就会引向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
他认识到,这一结论与我们日常的思考公正的方式不太一致:“我们有一种常识倾向,即认为收入、财富以及生活中的好东西,一般来说都应当根据道德应得而加以分配。公正就是依据德性而来的幸福……但现在,作为公平的公正反对这一观念。” [219]
罗尔斯通过质疑精英统治制度观点的前提,从而削弱了这一观点。这一前提就是:一旦我们消除了那些通往成功之路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障碍,我们就能说,人们应当得到他们的才能所带来的各种回报。
我们并不应得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正如我们不应得在社会中的最初起点一样。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得那种使得我们能够努力培养自己各种能力的优越品质—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早期所生活的幸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而这些则是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获取的。应得的观念并不适用于此。 [220]
如果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努力工作并按规则办事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他们的努力所获得的任何回报呢?不,并不完全是。罗尔斯这里在道德应得和他所谓的“对合法期望的应有资格”之间,做出了一个重要而细微的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与一种应得的主张不同,只有当已经有了某种游戏规则时,才能产生一种资格,它并不能事先告诉我们如何去确立各种规则。
在道德应得和应有资格这两者之间冲突的背后,暗含着诸多激烈的、关于公正的讨论:有些人认为,针对富人提高税率就剥夺了某些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或者认为,在大学录取时将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作为录取因素而加以考虑,就剥夺了那些持有SAT考试 (9) 高分的申请者们在道德上所应得的一种优势。而有些人则并不这样认为—人们在道德上并不应得这些优势,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游戏的规则应当是什么(如税率、录取标准)。然后我们才能说,谁有权利获得什么。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机会游戏和技能游戏之间的区别。假设我购买国家彩票,如果我的号码中奖的话,那么我就有资格获得我的奖品。可是我不能说我应得这份胜利,因为彩票是一种机会游戏。我的输赢与我的德性,或玩这一游戏的技能毫无关系。
现在让我们再做一个设想:波士顿红袜队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此之后,他们有资格获得战利品。他们是否应得这份胜利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其答案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打这场比赛的。他们是通过侥幸(如棒球裁判员在关键性时刻所发出的错误裁决)而赢得比赛的呢,还是他们实际上就是比对手打得好,展示了那些最能界定棒球的卓越与德性呢(如好的投球、及时的击球、漂亮的防守,等等)?
与机会游戏不同,在技能游戏中可能会有一种区别,即谁有资格拥有战利品和谁应得胜利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技能游戏奖励某些德性的运用与展示。
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与之相反,它涉及满足那些合法的期望—一旦游戏规则确立之后,这些合法的期望便会产生。一旦公正原则确立了社会合作的要求,那么人们就有资格获得他们在这些规则中所收获的利益。然而,如果税务体制要求他们交出一部分收入来帮助那些不利者,那么,他们不能抱怨说这剥夺了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某些东西。
因此,一个公正体系回答了人们有权要求什么的问题,满足了他们建立在社会制度之上的各种合法的期望。但是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并不与他们的内在价值成比例,也不依赖于他们的内在价值……并不涉及道德应得,分配的份额也并不倾向于要与它相称。 [221]
罗尔斯基于两个理由而反对将道德应得作为分配公正的基础: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拥有那些使我能够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地竞争的才能,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行为结果。可是,第二个偶然因素却同样具有决定性: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在道德上也同样具有任意性。即使我对自己的各种才能拥有唯一的、毋庸置疑的权利,可是事实仍然是:这些才能所获得的回报,将会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偶然性。在中世纪时期的塔斯卡尼,人们对壁画师极为看重,而在21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电脑程序设计师极为看重,如此等等。我的各种技能的收获好坏,取决于这个社会恰好想要什么。什么算作贡献,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
让我们来考虑以下这些工资上的差异:
· 美国教师每年的平均工资大约为43 000美元,午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戴维·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每年大约挣3 100万美元。
· 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年薪为217 400美元,而出演一档写实电视节目的“法官朱迪”(Judge Judy)每年挣2 500万美元。
这些工资上的差异公平吗?对罗尔斯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源于一种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们的税务体制和再分配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莱特曼和“法官朱迪”就有权利获得他们的收入。可是我们不能说,“法官朱迪”应得那比首席大法官罗伯特高出100倍的工资,或莱特曼应得那比学校教师高出700倍的工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恰好生活于一个在电视明星身上出手阔绰的社会—是他们的好运气,而不是某些他们应得的东西。
成功人士经常忽视他们的成功所具有的这一偶然性的方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幸运地拥有—至少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所恰好看重的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企业家的驱动力很有利;在一个官僚制度的社会,能轻易平和地与领导相处很有利;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社会,在电视上看起来不错、说话简短、嗓音有感染力很有利;在一个法治社会,去法学院深造、拥有能帮你在法学院入学考试中获得高分的逻辑和推理技能,会很有利。
我们这个社会看重这些事物的这一事实,并非我们的行为结果。假如拥有这些才能的我们,并不是生活于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喜欢诉讼的社会,而是生活于一个狩猎的社会、尚武的社会,或一个将最高的奖励和特权都授予那些展示了其身体力量或宗教虔诚的人们的社会,这时我们的才能会变成什么呢?很显然,它们不会让我们发展得太好。并且毫无疑问,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发展一些其他的才能。可是,我们会比现在具有更少的价值或德性吗?
罗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能会少获得一些,而且很可能如此。但是,在我们对较少的东西拥有权利的同时,我们不会比他人具有更少的价值和更少的道德应得。这一点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那些缺少某些特权地位,以及拥有较少这个社会所恰好奖励的各种才能的人而言,同样是真实的。
因此,当我们有资格获得游戏规则所承诺的、由于运用才能而得到的那些利益时,要是认为我们首先应得一个看重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才能的社会的话,那就是一种错误和自负。
伍迪·阿伦(Woody Allen)在电影《星尘往事》(Stardust Memories)中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阿伦在其中扮演一名与自己很相像的角色—一个名叫桑迪的著名喜剧演员。他遇见了往日邻居中的朋友杰里,后者因为当出租车司机而苦恼不堪。
桑迪 :你做什么?你干什么的?
杰里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开出租车。
桑迪 :哦,你看起来很不错。你……开出租车没什么不好。
杰里 :是啊,可是与你相比,再看看我……
桑迪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以前在邻居里我是那个爱开玩笑的孩子,对不对?
杰里 :没错。
桑迪 :所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我们生活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视玩笑的社会,你知道吗?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思考这件事的话—(清清嗓子)如果我是一个阿帕契亚印第安人的话,那些人根本就不需要喜剧演员,对吗?那样我就会失业。
杰里 :是吗?得了吧,这并不能使我感觉好点儿。 [222]
这个喜剧演员关于名声和财富的道德任意性的即兴解释,并没有打动该出租车司机。将自己的下下签看做一种坏运气,并不能使他减轻痛楚。也许这是因为,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世间的成就反映出我们所应得的。要消除这一观念并非易事。分配公正是否能够脱离于道德应得,这是一个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问题。
1980年,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竞选总统时,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妻子罗丝合著并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本书为自由市场经济做出了大胆热烈、毫不胆怯的辩护,并且在里根时代成为一部教科书—甚至是一首颂歌。在维护政府放任主义的原则不受到平等主义的反驳时,弗里德曼做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让步。他承认,那些成长于富裕家庭并进入名校上学的人,要比那些来自于拥有较少特权的背景中的人,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他还承认,那些拥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尽管这不是他们自己行为的结果—要比其他人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然而与罗尔斯不同,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当试着去纠正这种不公平。相反,我们应当学会去适应它,并享受它所带来的益处:
生活是不公平的。如果认为政府能够纠正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确实很吸引人。但是认识到以下这点也同样重要:即我们从自己所强烈反对的这种不公平中获得了多少利益。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天生拥有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拳击手的技能……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穆罕默德·阿里一夜能挣好几百万美元,这当然也不公平。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种抽象的平等理想,而不允许穆罕默德·阿里在一个晚上的比赛中所挣的钱,比那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做一天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所挣的更多,那么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们而言,难道不是更加不公平吗? [223]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反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自鸣得意式的建议。在一个鼓舞人心的段落中,罗尔斯表达了一个人所熟知,却经常被我们忘却的真理:事物所是的方式,并不决定它们应当所是的方式。
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224]
罗尔斯建议我们这样来处理这些事实:同意“与他人分享命运”,并且“只有当利用那些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能够有利于整体时,我们才能这么做”。 [225] 无论他的公正理论最终能否成功,它都代表了美国政治哲学中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具说服力的、支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
谢里尔·霍普伍德(Cheryl Hopwood)来自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她由一个单身妈妈抚养成人,并努力读完了中学、社区大学以及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州州立大学。然后她移居得克萨斯州,并申请就读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这是得州最好的法学院,也是全美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尽管霍普伍德的年平均分为3.8,并且在该法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表现也还不错(第83个百分位),可是她没有被录取。 [227]
霍普伍德是个白人,她认为自己被拒绝是不公平的。有些被录取的申请者是非洲裔的美国学生和墨西哥裔的美国学生,他们比她的大学成绩低,入学考试分数也没有她高。该学院有一个反歧视的政策,该政策偏向那些少数民族的申请者。事实上,所有与霍普伍德的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差不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都被录取了。
霍普伍德将自己的情况上报至联邦法院,声称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该大学回应称:其法学院的部分任务在于,增加得克萨斯州法律职业(不仅包括法律事务所,也包括州立法部门以及法庭)中的种族多样性和民族多样性。“一个公民社会中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社会愿意接受它的裁决。”该法学院院长迈克尔·沙洛特(Michael Sharlot)说道,“如果我们看不到各类团体的成员都在司法行政部门中起作用,那么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一目标。” [228] 在得克萨斯州,非洲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40%,可是在法律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却要小得多。当霍普伍德申请的时候,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院运用了一项反歧视行动的录取政策,其目标在于从少数民族的申请者中录取该班级中大约15%的成员。 [229]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该大学给少数民族的申请者们设定了比非少数民族申请者们要低的录取标准。然而,该大学的领导们声称,所有被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是合格的,并且他们大多数人都顺利地从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可是这对霍普伍德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安慰,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应当被录取。
霍普伍德对于反歧视行动的挑战,并不是首例上告到法院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30多年来,法院就一直在与反歧视政策所引发的各种棘手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作斗争。1978年,在“巴克案”(Bakke case) (10) 中,美国最高法院勉强支持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反歧视行动录取政策 [230] 。2003年,在涉及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一案中,最高法院以几乎对等的票数裁决:在录取时可以将民族作为一个考虑因素。 [231] 与此同时,加州、华盛顿州以及密歇根州的选民们最近自发地投票表决,反对在公共教育和就业领域中存在民族不平等待遇。
对于这些法庭而言,问题在于,反歧视行动的雇用和录取政策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所保证的“人人都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但是,让我们搁置宪法上的问题而直接关注这一道德问题:在雇用或大学录取时将民族和种族作为考虑因素,是否公正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反歧视行动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赞同将民族和种族纳入考虑因素的三个原因:纠正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补偿过往之错和促进多样性。
将民族和种族纳入考虑因素的原因之一就是:纠正标准化考试中可能存在的偏见。SAT考试和其他类似的、预测学术和职业成功可能性的考试,长期以来都遭到人们的非议。1951年,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博士项目的一位申请者,提交了一份很差的GRE分数。年轻的马丁·路德·金—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当时在语言表达能力测试中的分数低于平均分。 [232] 幸运的是,他还是被录取了。
有些研究表明,黑人学生和拉丁美洲裔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总体分数要低于白人学生,这甚至根据经济阶层而有所调整。可是,无论导致这种考试成绩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用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来预测学术上的成功与否,就需要人们在阐释这些分数时,考虑到学生的家庭、社会、文化以及教育上的背景。一个在南布朗克斯区就读于破旧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他在SAT考试中所得的700分,比曼哈顿东上城的一个就读于名牌私立学校的学生在SAT考试中所得的同样分数更有含金量。但是,在评估考试分数时考虑到学生们的民族、种族和经济背景,并没有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学院和大学应当录取那些拥有最好的学术前景的学生。它只是试图找出那种最精确的、衡量每个个体学术前景的标准。
真正与反歧视政策有关的争论,涉及另外两种理由—补偿的理由和多样性的理由。
补偿性的理由将反歧视行动看做对过往错误的一种纠正。它认为少数民族的学生应该得到偏爱,以补偿那段将他们置于一种不公正的不利处境的歧视史。这一论点主要将录取看做接受者的一种利益,并且试图以一种补偿过往的不公正及其残留影响的方式,来分配这种利益。
可是这种补偿性的论证遇到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批评者们指出,那些受益人未必就是那些曾经的受害者;那些提供补偿的人,也很少是那些造成所纠正之错误的人。许多反歧视行动的受益人都是中产阶级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并没有遭受贫民区中的那些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为什么一个来自于富裕的休斯敦郊区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应当比谢里尔·霍普伍德占有优势呢?后者可能实际上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经济困难。
批评者们认为,如果反歧视行动的要点在于帮助那些不利者,那么它应当基于阶层而不是种族。如果种族偏好意在补偿历史上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的不公正,那么从像霍普伍德这样的人这里强行索取补偿又怎么能说是公平的呢?他们在这些不公正的行为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支持反歧视行动的补偿性理由是否能够回答这一反驳,取决于“集体责任”这一令人费解的观念:我们是否具有一种道德责任来纠正前一辈人所犯下的错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道德责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是仅仅作为个体来承担责任呢,还是某些责任要求我们作为具有历史身份的共同体的成员来承担?由于我们在本书的后面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让我们此刻先搁置这个问题,而转向那种多样性的理由。
支持反歧视运动的多样性理由,并不依赖于具有争议性的集体责任的观念;它也不依赖于证明那些在录取时受到偏爱的少数民族学生本人遭受过歧视或阻碍。它并不将录取看做对接受者的奖励,而是看做一种促进社会上值得追求的目标的手段。
这种多样性的理由是一种以“共同善”为名义的理由—学校本身的共同善,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的共同善。首先,它认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学生团体是值得欲求的,因为它使得学生们相互之间,能够比他们都来自于相似的背景要学习得更多。正如一个来自于国内同一个地方的学生团体,会限制其理智上和文化上的观点一样,一个反映出相同民族、种族和阶层特征的学生团体,也会限制其理智上和文化上的观点。其次,这种多样性理由坚持认为,使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具备那种在重要的公共领域和职业角色中担任重要位置的能力,推进了该大学的公民目标,并对共同善做出了贡献。
这种多样性的理由,是众多大学和学院最经常提出的理由。当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院长面临霍普伍德的挑战时,他援引了他们学校的反歧视行动政策所要达到的公民目的。该法学院的部分使命就在于帮助增加得克萨斯州法律职业中的多样性,并使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能够在政府和法律部门承担领导性的角色。他认为,通过这种手段,该法学院的反歧视行动项目是成功的:“我们看到,我们那些少数民族的毕业生或被选为政府官员,或在优秀的法律事务所工作,或成为得克萨斯州立法机关和联邦法官的成员。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如果在得克萨斯州的重要部门有少数民族,那么他们通常是我们的毕业生。” [233]
当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巴克案”的时候,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作为与案件无关而被法官要求提供意见的第三者,提交了一份简短的说明,它出于教育的原因而维护反歧视行动。 [234] 它说明,成绩和考试分数从来都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如果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唯一的或占主导性的标准,那么哈佛学院就将失去很多活力和理智上的卓越成就……给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背景的品质也会受损。”在过去,多样性曾经意味着“学生们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城市居民和农场小伙子,小提琴家、画家和足球运动员,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有潜力的证券经纪人、学者和政客”。现在,哈佛学院也关心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
一个来自于爱达荷州的农场小伙子可以给哈佛学院带来一个波士顿人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同样的,一个黑人学生通常可以带来白人学生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哈佛学院中所有学生的教育背景的品质,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学生所带来的背景和观点上的差异。 [235]
多样性理由的批评者们提出了两种反驳—一种是实际性的,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那种实际性的反驳质疑反歧视行动政策的有效性。它认为,运用民族偏好并不会产生一个多元的社会或减少偏见和不平等,而会损害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尊、从各方面增加民族意识、加剧民族张力并在白人种族团体内部引发怨恨之声,他们感觉自己也应当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种实际性的反驳并不认为反歧视行动是不公正的,而是认为它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并且有可能弊大于利。
那种原则性的反驳认为,无论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班级或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具有多大的价值,也无论反歧视行动政策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有多成功,在录取中将民族或种族作为一种考虑因素就是不公正的。原因如下:这样做侵犯了像谢里尔·霍普伍德这样的申请者的权利,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却被置于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
对于一名功利主义者而言,这种反驳不会具有太多的分量。支持反歧视行动的理由,将仅仅取决于权衡它所产生的教育的和公民的利益是否高于它所导致的像霍普伍德和其他处于被淘汰边缘的白人申请者们的失望。可是许多反歧视行动的拥护者们并非功利主义者,他们是康德式的或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即使是值得欲求的目的也不能践踏个体权利。对他们而言,如果在录取中将民族作为一种考虑因素侵犯了霍普伍德的权利,那么这样做就是不公正的。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kin)是一位以权利为导向的法学哲学家,他认为在反歧视行为政策中运用民族偏好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并以此与这种反驳对质。 [236] 他质问道,霍普伍德的什么权利被否定了呢?可能她认为,人们有权利不被一些超越于他们掌控的因素(如民族)而评判。可是,大多数大学传统的录取标准都涉及一些超越于人们掌控的因素。我来自于马萨诸塞州而不是爱达荷州,或者我是一个糟糕的足球运动员,或者我五音不全,这都不是我的错。我没有能力在SAT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也不是我的错。
可能这里受到威胁的权利是这样一种权利,即那种仅仅根据学术标准—而不是因为善于踢足球、来自于爱达荷州、在救济院当过志愿者等—而被考量的权利。基于这种观点,如果我的成绩、考试分数以及其他学术前景的衡量标准,将我置于申请者的顶层,那么我就应当被录取。换言之,学校应该仅仅根据我的学术实力考量我。
可是,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权利。有些大学可能仅仅根据学术资格而录取学生,不过大多数大学并非如此。各个大学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录取标准。德沃金认为,没有哪一个申请者拥有以下权利,即:该大学以一种首先奖励某些特殊才能的方式—无论是学术技能、运动才能还是其他—来设定自己的使命和规划自己的录取政策。一旦这所大学设定了自己的使命,并设置了录取标准,那么,只要你比其他申请者更加符合这些标准,你就拥有一种被录取的合法期望。那些位于前列的申请者们—算上学术前景、种族和地理的多样性、体育特长、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有资格被录取,将他们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可是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拥有根据一系列标准被考量的权利。 [237]
在反歧视政策的多样性理由的核心,存在着一种有争议但却深刻的主张:录取并不是一种授予最高美德或德性的荣誉。那些拥有最高考试分数的学生,以及来自于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团体的学生,在道德上都不应得录取资格。只要申请者对满足该大学的社会目的有所贡献,那么他的录取资格就是正当的,而并不是因为它奖赏学生们的那些被单独界定的优点与美德。德沃金的重点在于:录取中的公正并不是在奖赏优点与德性,只有当一所大学界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才算是分配大学新生名额的公平方式。该使命界定了相关的美德,而不是相反。德沃金关于大学录取的论证,与罗尔斯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证类似,它与道德应得无关。
这是否就意味着,各个学院能够自由地、如其所愿地界定自己的使命呢?是否任何一种与这种声明的使命相符合的录取政策就是公平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久前美国南部的一些校园中的种族隔离又如何呢?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曾经刚好处于早期对宪法提出质疑的中心地带。1946年,当这个学校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它拒绝录取希曼·马里昂·斯韦特(Heman Marion Sweatt),原因是该学校不录取黑人。他的挑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斯韦特诉佩因特案” (1950),这给了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一记重棒。
然而,如果录取政策公平性的唯一衡量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于该学校的使命,那么,得克萨斯法学院在当时提出的论点又有什么问题呢?它的使命就是为得克萨斯法律事务所培养律师。该法学院认为,由于得克萨斯法律事务所当时并不雇用黑人,那么录取黑人就不能满足该学校的使命。
你可能会争论说,作为一所公立学校,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在使命的选择范围上应当比私立学校更广。当然,那些著名的在宪法上对高等教育中反歧视政策的挑战,确实涉及了一些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巴克案”)、得克萨斯大学(“霍普伍德案”)以及密歇根大学(“格鲁特案”)。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试着判断使用民族偏好是公正还是不公正—而不是其合法性,因此,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
私立协会和公立团体都可能由于其不公正而受到批判。让我们回忆一下,在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那些室内静坐的抗议者们坐在午餐柜台前面,抗议种族歧视。这些午餐柜台是私人拥有的,尽管如此,他们所实施的种族歧视却是不公正的。(事实上,1964年的《民权法案》确认了这种歧视是非法的。)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些常春藤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正式或非正式采用的反犹太人制度。是否仅仅因为这些学校是私立的而非公立的,这些制度在道德上就是可辩护的呢?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以减少反犹太人的名义提议,要将犹太人的录取率控制在12%。“学生中反犹太人的情绪日益高涨,”他说,“这种情绪的高涨与犹太人数量的增长成正比。” [238] 20世纪30年代,达特茅斯学院的招生办主任给一位抱怨校园里犹太人人数增长的校友写了一封回信。“我很乐意接受你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评论,”这位主任写道,“如果在1938年这个班上的犹太人超过了5%或6%,那么,我的悲恸之情将无以言表。”1945年,达特茅斯校长援引该学校的使命为限制录取犹太人作辩护:“达特茅斯是一所基督教学院,其建立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们信仰基督教。” [239]
如果像支持反歧视行动的多样性理由所认为的那样,大学可以设定任何促进其所界定的使命的录取标准,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谴责种族主义的排斥和反犹太人的限制呢?在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地区使用民族偏好来排除人们,与当今的使用民族偏好来录取人们的反歧视行动,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吗?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得克萨斯法学院将种族当做一种低劣的标志,而如今的种族偏好则并没有侮辱或污蔑任何人。霍普伍德认为自己被拒绝是不公平的,可是她不能说这表达出一种仇恨与蔑视。
这是德沃金的回答。种族隔离时期的种族排外基于“这样一种卑劣的观点—一个民族可能内在地比另外一个民族更有价值”。而反歧视政策则并不涉及偏见,而只是主张,考虑到在关键职业中促进多样性的重要性,黑人或拉丁美洲裔人“可能有一种社会性的有用的特征”。 [240]
像霍普伍德这样被拒绝的申请者,可能并不会觉得这一区别是令人满意的,不过这确实具有一种特定的道德力量。该法学院并不是说霍普伍德更加低劣,或那些代替她而被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应得一种优势而她不应得。它只是说,班级和法院里的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满足了该法学院的教育目的。除非对这些目的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那些失败者的权利,否则那些失望的申请者们就不能合法地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有一个关于多样性论点的测试:它有时候能为白人的种族偏好作辩护吗?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小星城”(Starrett City)的情形。这套楼群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有两万名居民,是全美最大的由政府资助的中等收入者住房项目。它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目的在于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社区。它通过使用“占有率控制”而达到这一目的,“占有率控制”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的人口限制在总数的40%,试图平衡该社区的民族和种族的构成。简言之,它使用了一种定额体制。这种定额并不是建立在偏见和蔑视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于城市经验的关于民族“临界点”的理论基础之上。该项目负责人希望避免这种临界点,后者导致了其他社区中的“白人逃跑”现象,并破坏了民族融合。通过维持民族和种族的平衡,他们希望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具有民族多样性的社区。 [241]
这起到了作用。该社区变得令人非常满意,许多家庭都想搬进来,于是“小星城”便确立了一份等候名单。部分地由于那种定额体制—后者分配给非洲裔美国人的公寓要比分配给白人的少—黑人家庭不得不比白人家庭等更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白人家庭必须等3~4个月以获得一套公寓,而一个黑人家庭则需要等上两年。
那么,这里的定额体制偏袒白人申请者—这并不是基于种族的偏见,而是基于“维持一个民族融合的社区”这一目标。有些黑人申请者发觉这种有意识的种族政策是不公平的,并提起了一项种族歧视的诉讼。在其他情形中支持反歧视政策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协议允许“小星城”保留其定额体系,同时要求该州增加少数民族进入其他住房项目的机会。
“小星城”分配公寓的有意识的种族方式,是否公正呢?不,除非你接受了支持反歧视行动的多样性理由。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在住房项目和大学教室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在此处受到损害的事物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共存亡。如果多样性满足了共同善,并且没有人基于仇恨和蔑视而受到歧视,那么,民族偏好就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罗尔斯关于道德应得的观点,没有人能根据自己那些被独立界定的优点,而应得一所公寓或新生班级中的一席之地。只有当住房管理人士或学校领导设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才能确定什么才算是优点。
拒绝承认道德应得作为分配公正的基础,这在道德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打消了存在于精英统治制度的社会中,为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妄想:成功乃美德之冠,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加应得。正如罗尔斯所提醒我们的:“没有人应得更好的自然能力,在社会中也不应得一个更好的起点。”我们居住于一个恰好奖励我们特殊强项的社会也并非自己所为,这是对我们好运气而非德性的一种衡量。
隔断公正与道德应得之间关联的令人不安之处,并不容易描述。“工作与机会是对那些应得者的奖励”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可能在美国比在其他社会更加深入人心。政治家们经常宣称那些“努力工作并按规则行事”的人应当能够跻身于社会前列,并鼓励那些实现了自己美国梦的人将自己的成功看做其美德的折射。这一观念至多是一种混合性的鼓励,其持续性存在对于社会稳定性来说是一种障碍。我们越多地将自己的成功看做自己的行为结果,那么我们就越少地感觉到自己对那些落后者所负有的责任。
可能这种持续性的观念—成功应当被看做对德性的奖励—就是个错误,是一个我们应当努力消除的神话。罗尔斯关于财富的道德任意性的论点,强有力地对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可是,从政治上和哲学上来说,我们不可能使关于公正的论证,像罗尔斯和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决然地脱离于关于应得的争论。下面让我来解释原因。
首先,公正通常具有表示敬意的一面。关于分配公正的争论并不仅仅与谁得到了什么有关,同时也与什么品质值得尊敬和奖励有关。其次,“只有当社会制度确立了自己的使命时,优点才会产生”的这种观念,容易遇到以下复杂的情形:在关于公正的争论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机构—如学校、大学、职务、职业、公共职务等—并不能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任意方式来界定自己的使命。这些机构至少部分地由它们所推崇的独特的善所界定。我们仍然有余地来讨论,在特定时刻,一所法学院、一支军队或一支管弦乐队的使命应当是什么,可是与此同时,并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特定的善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适应,忽视这些善在分配中的作用可能就是一种腐败。
通过回忆霍普伍德的案例,我们可以看清楚公正与荣誉交织在一起的方式。让我们假设德沃金是对的,即谁应当被录取与道德应得并无关联。以下是那所法学院应当发给霍普伍德的拒绝信: [242]
亲爱的霍普伍德小姐:
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录取申请被拒绝了。请你谅解,我们的决定丝毫没有冒犯之意。我们并没有蔑视你,事实上,我们甚至认为你跟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同样应得。
你进入了一个碰巧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各种才能的社会,这并非你的过错。那些取代你而被录取的人,并不应得一席之地,也并不因为那些使他们能够被录取的因素而值得表扬。我们仅仅是将他们—和你—作为一种满足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的工具来考量。
我们知道你会觉得这一消息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你的失望不应当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夸大,即:这种拒绝以某种方式反映出你的内在道德价值。我们在以下一种意义上对你表示同情:当你申请的时候,你恰好没有拥有社会所恰好需要的那些特征,这太糟糕了。祝你下次好运。
你真诚的……
以下是某所在哲学上直言不讳的法学院,给那些被录取的学生们所发送的、缺乏尊敬意味的录取信:
亲爱的成功的申请者: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你的录取申请被接受了。结果表明,你恰好拥有社会现在需要的那些特征,因此,我们打算通过让你学习法律,而利用你的资质以满足社会的利益。
你值得祝贺,但是并不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你拥有那些使你被录取的各种品质而应得奖励—你并不应得—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彩票的中奖者应当得到祝贺。你在恰当的时机获得了恰当的特质,这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你选择接受我们的邀请,那么你最终将有资格获得一些利益,因为你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发挥你的潜力。你应该为此而庆祝。
你—或更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想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庆祝,即你认为,这次录取如果不是有力地反映出你的天赋的话,那么也至少反映出你培养这些能力时所付出的有意识的努力。然而,“你应得那些对你的努力而言非常必要的优秀品格”这一观念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品格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幸运的环境,而这些你是没有资格拥有的。应得的观念在此并不适用。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待着与你相见于金秋时节。
你真诚的……
这样的信可能会缓解那些被拒者们的痛苦,并打击那些被接受者们的狂妄自大情绪。那么,为什么大学仍然发送(申请者们也期望)一些充满着祝贺和尊敬修辞的录取信呢?可能是因为各所大学不能完全消除这样一种观念—它们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促进某些目的,同时也在于尊敬和奖励某些德性。
这将我们引入了第二个问题,即:学院和大学是否能够随其所愿地界定自己的使命。让我们暂时搁置民族和种族偏好,而考虑另一种反歧视政策的争议—关于“遗赠偏好”(legacy preference)的争论。许多学校允许校友的孩子们在录取时占有优势,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设社区和学校精神;另一个理由就是,希望那些感激涕零的校友父母,为他们的母校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
为了鼓励这个经济上的理由,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大学所说的“发展性的录取者”(development admit)—指那些并非校友的孩子,但都是拥有富裕的、能够给学校提供数目可观的经济贡献的父母的申请者们。许多大学录取这些学生,即使他们的成绩和考试分数没有所要求的那样高。为了将这一观念发展至极致,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大学决定将新生班级中10%的名额拍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
这种录取制度是否公平呢?如果你认为,优点仅仅意味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学校的使命作贡献的能力,那么答案将是肯定的。无论其使命是什么,所有的大学都需要钱来完成这一使命。
借助于德沃金关于优点的宽泛定义,一个被某个学校为了100万美元建设校园新图书馆的馈赠而录取的学生,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入学满足了大学这个整体的善。那些由于慈善家的孩子而被拒绝的学生,可能会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德沃金对霍普伍德的回应对他们同样适用。公平所要求的是:没有人由于偏见和蔑视而被拒绝,申请者们由那些与大学为自己所设定的使命相关的标准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条件得到了满足。那些失败的学生并非偏见的受害者,而只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没有愿意并有能力捐赠一座图书馆的父母。
可是这一标准太无力了。富裕的家长们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购买一张通往常春藤学校的门票,这似乎仍然是不公平的。可是,这种不公正由什么组成呢?不会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来自于贫困或中产家庭的申请者们被置于一种超越于他们掌控的不利处境。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很多超越于我们掌控的因素在录取时都是合法的因素。
可能这种拍卖的问题之处与申请者的机会无关,而与该大学的整体性有关。将座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对于一场摇滚音乐会或体育比赛来说要比教育机构更加合适。正当地分配某一事物的方式,可能与这个事物的本质及其目的相关。反歧视政策的争论反映出不同的关于“大学是为了什么”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应当追求学术上的卓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应当追求公民美德,以及该如何平衡这些目的。尽管一种大学教育达到了为学生们通往成功生涯做准备的目的,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商业性的。因此,将教育当做一种消费品加以出售,就是一种腐败。
那么,什么才是大学的目的呢?哈佛并不是沃尔玛,也不是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其目的并不是要使财政收入最大化,而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服务于共同善。教学和研究确实花销很大,各所大学也都投入了很大精力来筹集资金。但是,当挣钱的目标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影响到录取工作时,那么这所大学就远远偏离了学术和公民的善,而后者是其存在的首要原因。
“大学入学名额分配中所体现出的公正,与大学所适当追求的善有关”这种观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难将公正和权利的问题脱离于荣誉和德性的问题。大学授予荣誉学位,以祝贺那些展示了大学所要推进的各种德性的人们。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所授予的每一个学位都是一种荣誉学位。
那种将关于公正的论点与关于荣誉、德性以及善的意义的论点联系在一起的尝试,看起来似乎是解决那种毫无希望的分歧的一剂良方。人们对荣誉和德性持有不同的观点。各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大学、公司、军队、职场还是一般性的政治共同体—都是有争议的和令人担忧的。因此,为公正和权利寻求一种远离于这些争论的基础,是有诱惑力的。
许多现代政治哲学都试图这样对待公正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和罗尔斯的哲学,都大胆地试着为公正和权利找到一种基础,这一基础中立于各种不同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点。现在是时候看看他们的谋划是否成功了。
考利·斯马特(Callie Smartt)是西得克萨斯安德鲁中学的一名非常受欢迎的拉拉队队长。她患有大脑瘫痪症,只能借助于轮椅四处走动,可这一事实并没有抑制那种由于她出现于高三代表队的比赛现场,而在橄榄球运动员和球迷们中所激起的热情。但是,这次赛季之后,考利却被踢出了拉拉队。 [241]
在其他拉拉队队员及其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学校领导告诉考利,来年要是还想参加拉拉队的话,她将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在一套严格的常规体育项目中参加选拔,内容包括劈叉和翻筋斗。该拉拉队主队长的父亲强烈反对考利参加拉拉队,他说他担心考利的安全。但是考利的妈妈则猜疑,他们是对考利所获得的欢迎心存怨恨,因而产生这种反对的。
考利的故事引发了两个问题。其一为公平问题。学校应当要求她去参加体育项目以便合格地成为一名拉拉队队长吗?或者,考虑到她的残疾,这一要求是不是不公平的呢?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援引不歧视原则:只要考利能在该位置发挥好作用,那么就不能仅仅因为她—尽管这不是她自己的过失—缺乏身体能力来完成常规的体育项目,而将她排除在拉拉队之外。
可是这种不歧视原则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它回避了此争论的核心问题:扮演好拉拉队队长这一角色意味着什么?考利的竞争对手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拉拉队队长,你就必须会劈叉和翻筋斗。毕竟,这是拉拉队队长让观众兴奋起来的传统方式。而考利的支持者们则认为,这将拉拉队队长的目的,与一种达到目的的方式混淆了起来。拉拉队队长的真正目的在于,激励学校精神并使那些球迷活跃起来。当考利在轮椅中上下欢呼、挥舞着球花并绽放灿烂笑容的时候,她很好地做到了拉拉队队长所需要做的事情—点燃观众的激情。因此,为了决定拉拉队队长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需要决定,对于拉拉队而言,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才是次要的。
考利的故事所引发的第二个问题与怨恨有关。什么样的怨恨可能刺激拉拉队主队长的父亲呢?为什么考利在拉拉队中的存在让他备受困扰呢?不可能是考利的加入剥夺了他自己女儿的一席之地,他的女儿已经在拉拉队中了;也不仅仅是他可能对一个在常规体育项目中超过自己女儿的女孩所感到嫉妒,考利当然并没有这样。
以下是我出于直觉的想法:他的怨恨很可能反映出一种感觉,即:考利被授予一种她不应得的荣誉,这以某种方式嘲笑了那种由于其女儿领导拉拉队的专长,而给他带来的骄傲感。如果出色的领导拉拉队的工作能够在轮椅上完成,那么,那些在翻筋斗和劈叉方面非常出色的人所获得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便受到了贬低。
如果考利之所以应当成为一名拉拉队队长,是因为她尽管残疾,却展现了与这一角色相适合的美德,那么,她所获得的荣誉,确实对其他拉拉队队长所获得的荣誉构成了某种威胁。她们所展示的体育技能,在成功地领导拉拉队这一事务当中似乎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而只是使观众兴奋的方式之一。这名主队长的父亲尽管不是那么宽宏大量,但他却正确地把握了那些受到威胁的东西。多亏了考利,一种曾经被看做具有特定目的、其所授予的荣誉也是固定的社会行为,现在被重新定义了。她展示出,有不止一种方式来成为一名拉拉队队长。
我们要注意,这与公平有关的第一个问题,和那种与荣誉和怨恨有关的第二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为了判定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分配拉拉队的领导位置,我们需要判定领导拉拉队的本质和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说,哪些品质对它而言必不可少。可是,决定领导拉拉队的本质可能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使我们卷入一些关于什么品质值得尊敬的争论之中。什么算作领导拉拉队的目的,部分地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样的德性应得承认和奖励。
正如本章所要展示的,类似于领导拉拉队这样的社会行为,不仅仅只有一种工具性的目的(鼓舞拉拉队),同时也有一种荣誉性的或模范性的目的(庆祝某种卓越或德性)。在选择自己的拉拉队队长的时候,高中学校不仅仅是在促进学校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它希望学生们去钦佩和学习的品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争论是如此激烈的原因,这也解释了那令人困惑之处—那些已经在拉拉队之中的学生(及其家长)在考利的合法性的争论当中,如何能感觉到一种危及自身的危险。这些家长希望拉拉队队长这一位置,能尊重自己女儿所拥有的那些传统拉拉队队长所具有的德性。
以这种方式来看,西得州关于拉拉队队长的纷争,就是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一种缩写。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两种观念,两者都体现于关于考利的争论当中:
1. 公正是目的论的。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行为的目的(telos,意图、目标或本性)。
2. 公正是荣誉性的。为了推理一种行为的目的—或讨论之,就至少要部分地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
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键在于,弄明白这两种考量的力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
现代的各种公正理论,都试图将公平和权利的问题与荣誉、德性和道德应得的问题分离开来。它们寻求那些中立于各种目的的公正原则,并使人们能够自己选择和追求他们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并不认为,公正可以以这种方式保持中立。他认为,关于公正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就是关于荣誉、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
弄明白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与良善生活必然相关,将会帮助我们弄明白那种企图分开这两者的努力所具有的危险。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可是,什么才是一个人所应得的呢?优点与应得之间相关联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取决于我们要分配什么。公正包括两个因素:“物品以及分配得到这些物品的人”。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那些同等之人应当分配得到同等之物”。 [242]
可是这里便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哪个方面平等呢?这取决于我们在分配什么,取决于那些与被分配物品相关的美德。
假设我们在分配长笛,那么,谁应当得到最好的长笛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那些最好的长笛吹奏者。
公正根据优点,根据相关的卓越而有差别地对待。在吹长笛这一情形中,相关的优点就是那吹得好的能力。如果基于任何其他的因素,如财富、贵族身份、身体上的美丽以及机会(抽奖)等,而有差别地对待的话,那将是不公正的。
贵族身份及美貌,与吹长笛相比而言,可能是更大的优势。那些拥有这些优势的人,总的来说,可能在这些方面要超过那个长笛演奏者,这比该长笛演奏者所超越于他们的地方要多。可是,此处的事实仍然是:他是那个应当得到长笛的最佳人选。 [243]
在广阔的、不同的维度来比较各种优越性就有很多可笑之处。如果这样询问的话会毫无意义:“我是不是比作为一个优秀的长曲棍球运动员的她更帅?”或者,“贝比·鲁斯(Babe Ruth)与身为作家的莎士比亚相比,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棒球运动员?”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仅仅作为室内游戏才有意义。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在分配长笛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寻找那些最富有的、最好看的,甚至各方面来说最好的人,而是应当寻找最佳的长笛吹奏者。
人们对这一观念非常熟悉。许多管弦乐队在幕后进行试听会,以便人们不带偏见或干扰地对音乐的质量进行评判。可是,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理由却不甚熟悉。将最好的长笛给最佳长笛吹奏者的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产生最好的音乐,对我们听众有利。然而,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由。他认为,最好的长笛应当归给最佳长笛吹奏者的理由是,这是长笛存在的目的—被很好地吹奏。
长笛的目的在于产生动听的音乐,那些能够最佳地实现这一目的的人,就应当拥有最好的长笛。
同样真实的是:将最好的乐器给予最好的音乐家会带来受人欢迎的结果—产生最好的音乐,这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也就是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最大幸福。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亚里士多德的理由超越了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
他从一个物品的目的,推导出该物品恰当的分配方式;他的这种推理方式,是目的论推理的一个例子。[“目的论”(Teleological)源自希腊语telos,意指意图、目的或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决定某物品的正当分配方式,我们需要研究被分配之物的目的或意图。
目的论的推理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思考公正的方式,但它确实具有某种合理性。假设你不得不决定如何去分配使用某大学校园里的网球场,你可能会设定一个高额费用,而给那些能支付最高价格的人以优先权;或者你可能会将优先权给予校园里的那些大人物—如学校校长,或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两位著名的科学家正在打一场水平很一般的网球,他们几乎都不能将球打过网;这时,校网球队走了过来,想要使用这个球场。难道你不会说,这两位科学家应当转移到一个差一点的网球场去,以便校网球队队员能够使用最好的网球场吗?你此时的理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最好的网球运动员能够最佳地利用最好的网球场,而最好的网球场对于那些平庸的网球运动员来说是一种浪费。
或者让我们假设,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Stradivarius)正在待售,一位富有的收藏家的出价要高于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这位收藏家想要把这把小提琴挂在客厅作展示。难道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损失,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公正吗?—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拍卖不公平,而是这一结果不合适。在这种反应背后可能潜藏着一种(目的论的)思考,即: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是用来演奏的,而不是用来展示的。
在古代,目的论的思维方式比在当今更加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焰之所以向上蹿,是因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乡,石头之所以往下落,是因为它们在奋力接近地球—这是它们的所属之地。人们将自然看做拥有某种意义的秩序。要理解自然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就要抓住它的意图和本质性的意义。
随着现代科学的来临,自然不再被看做一种有意义的秩序。相反,它开始被机械地理解,受制于物理法则。将自然现象用各种意图、意义和目的来加以解释,现在会被看做一种天真幼稚或拟人化比喻。尽管有这种转变,可是将这个世界看做有目的论秩序、看做一个有意图的整体的这种诱惑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持续存在着,尤其是在孩子们中间,他们接受教育不要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当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在给他们读A·A·米尔恩(A. A. Milne)所著的《小熊维尼》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种孩子般的观点—自然充满神奇和魔力,是由意义和目的所推动的。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小熊维尼走进森林,来到一棵大橡树下。从这棵树的顶端,“传来了一阵阵嗡嗡的声音”。
小熊维尼坐在树下,用两只爪子托住脑袋开始思考。
首先它在想:“这种嗡嗡的声音意味着某种东西。你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只是这么嗡嗡在响,而不意味着某种东西。如果有嗡嗡的声音,就有人在制造这种嗡嗡的声音。我知道,有这种嗡嗡声音的唯一原因就在于你是一只蜜蜂。”
然后它又想了很长时间,说:“我知道,成为一只蜜蜂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酿蜜。”
接着,它站了起来,说:“酿蜜的唯一理由就是我能吃它。”于是它开始爬树。 [244]
小熊维尼那种孩子般的关于蜜蜂的思维方式,是目的论推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长大了而放弃了这种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而认为这种方式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却是离奇的。在科学领域拒绝了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之后,我们也倾向于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拒绝它。但是,在思考社会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时候,要想摒弃目的论的推理方式却并非易事。如今,没有哪个科学家拜读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或物理的著作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们。但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们,仍然在阅读和思考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与政治哲学。
关于反歧视行动的争论,可以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长笛的论点的回应,而被改写。我们开始于对公正分配标准的寻求:谁有权利被录取呢?在表达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至少含蓄地)在问:“一个大学的意图或目的,到底是什么?”
情况经常是这样的,目的经常并不明显却具有争议性。有些人说大学就是为了促进学术成就,因此学术上的前景应当是录取的唯一标准。而另一些人则说,大学的存在也应当服务于某些公民目的,因此,例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成为领导的能力,就应当成为录取的标准之一。辨别一所大学的目的似乎对决定恰当的录取标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便凸显了大学录取公正问题目的论的一面。
与大学之目的的争论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关于荣誉的问题:大学要适当地尊敬和奖赏什么样的德性或成就?那些认为大学的存在仅仅要称赞和奖励学术上成就的人,很可能会反对反歧视政策;而那些认为大学的存在也应当促进某种公民理想的人,可能会很好地接受它。
那些自然地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关于大学、拉拉队队长以及长笛的争论,都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争论,经常都是关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意图和目的的争论,这反过来又反映出不同的、关于这一制度应当尊敬和奖励何种美德的观点。
如果人们在所讨论的行为目的或意图上存在分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是否有可能推理出一项社会制度的目的?或者说,大学的目的仅仅就是学校创始人或校管理委员会所声称的那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有可能推理出各种社会制度的目的,它们的本质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但也不仅仅是一个观点的问题。(如果哈佛学院的目的仅仅由创始人的意图所决定,那么其主要目的仍然是培训公理会的牧师。)
那么,我们怎么能在面对各种分歧的时候,推理出一种社会制度的目的呢?我们又如何引入那些与尊敬和德性相关的观念呢?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政治的讨论中,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他最连贯一致的回答。
当我们现在讨论分配公正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关于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分配。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分配公正并不主要涉及钱财,而是涉及职务和荣誉。谁应当拥有统治权?应当如何分配政治权威?
乍一看来,答案当然似乎同样明显:一人一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将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可是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所有关于分配公正的理论都具有歧视性。问题在于:哪一种歧视是公正的?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上述行为的目的。
因此,在我们说政治权利和权威应当被怎样分配之前,我们必须研究政治的意图或目的。我们必须提出疑问:“建立政党是为了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关心不同的事物。讨论一支长笛或一所大学的目的是一回事,尽管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分歧,可是它们的目的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一支长笛的目的与创造音乐有关;而一所大学的目的则与教育有关。然而,我们真的能判定政治行为的目的或目标吗?
如今我们不再认为政治拥有某种特定的、实质性的目的,而是认为政治应该考虑公民可能拥护的多种目标。这不就是我们拥护选举制度的原因吗—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选择那些他们集体想要追求的各种意图和目的?如果我们事先将某种意图和目的施加给政治共同体,那么就似乎取代了公民们自己作决定的权利;这样也有一种危险,即:将那些并非每个人都接受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我们不情愿赋予政治以某种特定的目的或目标,这反映出我们对个体权利的关心。我们将政治看做一种程序,它使每个人都能够选择自己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看。对他而言,政治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套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权利框架,而是要塑造好公民,培育好品质。
任何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须致力于促进善这一目的。否则,一种政党就沦为一个单纯的联盟……否则,法律也就变成一种联盟……“是对人们权利的一种担保”—而不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例如能使城邦的成员变得善良和公正的生活规则。 [245]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两种主要的、会对政治权威提出要求的制度—寡头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每种制度都有一种主张,不过都是部分的主张。寡头制认为,城邦应当由富人统治,而民主制则认为,出生自由是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标准。但是两者都夸大了各自的主张,因为他们都误解了政治共同体的目的。
寡头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政治共同体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财产和促进经济繁荣。如果它仅仅是为了这些目的,那么财产的拥有者就应得政治权威的最大份额。对于他们而言,民主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政治共同体不仅仅在于给大多数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民主制”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数主义。他反对这样一种观念:政治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各种偏好。
以上两者都忽视了政党的最高目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相互间的防御提供一种联盟……或疏通经济贸易以及推进经济交往”。 [246]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关系到某种更高的事物,它关系到试着怎样去过一种好生活。政治的目的完全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亚里士多德承认其他较低一级的联盟的有用性,如防御同盟和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联盟并不算做真正的政治共同体。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受限的。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组织,仅仅关心安全问题或经济贸易,它们并不构成一种可以塑造参与者品质的、共享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对一个仅仅关心安全问题和贸易而忽视对公民的道德和公民教育的城市或国家,做出同样的评论。“如果当他们聚集到一起后,其交往的精神仍然与他们分开的时候一样,”亚里士多德写道,“那么,它们的联盟就不能被真正地看做一个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247]
“一个城邦并不是居住于同一地区的居民的联盟,也不是为了防止相互间的不公正或疏通交易。”尽管这些条件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是必要的,但它们却并不是充分的。“一个城邦的目的和意图是良善生活,各种社会生活制度也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 [248]
如果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促进良善生活,那么,职务和荣誉的分配又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亚里士多德对待政治如同对待长笛一样:他从物品的目的来推理恰当的、分配它的方式。“那些对这种联盟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具有卓越的公民美德的人,也是那些最善于慎议共同善的人。那些具有最高公民成就的人—而并非那些最富有、数量最多的或最帅的人—就是那些应该得到最多的政治认可和影响力的人。 [249]
由于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生活,那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就应当归于像伯里克利(Pericles)这样的人,他们拥有最高的公民德性,并且最善于鉴定什么是共同善。财产的所有者应当有发言权,大多数人的考量应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但是,最大的影响力应当归于那些具有良好品质和判断力的人,以便决定是否与斯巴达作战,以及何时作战、如何作战。
像伯里克利(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之所以应当拥有最高职务和荣誉,不仅仅在于他们会执行明智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同时也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至少部分就是为了尊敬和奖赏公民德性。将公共认可赋予那些展示了公民成就的人,就满足了这个良好城市所起的教育性作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公正的目的论的一面,是如何与它荣誉性的一面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即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生活,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推断说:那些展示了最高公民德性的人,应当得到最高的职务和荣誉。但是,当他说政治就是为了良善生活时,他是否对呢?这最多是一种有争议性的主张。如今,我们一般将政治看做一种必要的恶,而不是良善生活的本质特征。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妥协、装腔作势、特殊利益和腐败。即使是政治的最理想的运用—作为达到社会公正的工具,作为一种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途径—也都是将政治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不是人类善的一个本质性的方面。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参与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过一种好生活而言必不可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下,完美地过一种好的、有德性的生活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源于我们的本性。只有生活在一个城邦之中并参与政治,我们才能完全地实现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注定为了政治联盟而存在,要比蜜蜂和其他群居动物更高级”。他所给出的原因如下:自然不会徒劳地创造任何事物,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类拥有语言能力。其他动物能发出声音,声音能够表明快乐与痛苦。可是,语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能力,它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出快乐与痛苦,还要声明何谓公正、何谓不公正,并在对错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并不是先默默地理解这些事物,然后再用词语表达出来;语言是我们识别、慎议善的介质。 [250]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有在政治联盟中才能使用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城邦中才与他人慎议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良善生活的本性。“我们因此明白,城邦出于自然而存在,并且要先在于个体。”他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如此写道。 [251] 他这里所说的“先在”是指功能上或目的上的先在,而非时间顺序上的先在。个体、家庭以及宗族存在于城市之前,可是只有在城邦之中,我们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本性。当我们孤独自处的时候,我们是不自足的,因为我们不能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慎议能力。
一个孤独自居的人—亦即一个不能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或由于自身已经自足了而不需要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并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因此肯定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 [252]
因此,只有当我们运用语言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与他人慎议什么是对与错、善与恶以及公正与不公正。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政治领域运用这种语言能力和慎议能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家庭、宗族或俱乐部里这样做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德性和良善生活所作的说明。尽管这一工作主要与道德哲学相关,但它却说明了德性的获得是如何与成为一个公民紧密相关的。
道德生活的目标是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并不是功利主义所说的意思—使抵消掉痛苦所剩下的那部分快乐最大化。有德性的人就是那个在正当之事中获取快乐和痛苦的人。例如,如果有人从观看斗狗中获得快乐,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克服的恶,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之源。道德上的卓越并不在于累计快乐与痛苦,而在于校正它们,以使我们从高尚的事物中获得快乐而从卑贱的事物中获得痛苦。幸福并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灵魂与德性相符合的行为”。 [253]
可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居住在一个城邦并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家里,或在一个哲学课堂上,或读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来学习正确的道德原则,然后在需要的时候运用它们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并不能以这种方式成为有德性之人。“道德德性产生于习惯的结果。”它是我们通过行动而学到的。“我们首先通过运用这些德性而获得它们,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艺术。” [254]
从这个方面来说,成为有德性之人就像学习吹奏长笛。没有人能够通过读一本书,或听一次讲座就学会怎样演奏一种乐器。你得去练习。聆听水平高超的音乐家演奏,并听出他们是如何演奏的,这很有用。可是,你不可能不拉小提琴就成为一名小提琴家。道德德性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而成为正当之人,通过有节制的行为而成为有节制之人,通过做勇敢的行为而成为勇敢之人。” [255]
这与其他行为和技能,比如烹饪,十分相似。市面上出版了很多烹饪类的书籍,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仅仅通过读这些烹饪书而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你得花很多时间练习烹饪。讲笑话是另外一个例子。你不能靠读笑话书和收集好笑的故事而成为一个喜剧家,也不能仅仅通过学习喜剧的原则而成为一个喜剧家。你得练习—练习节奏、时间、姿势以及语调—同时也要观摩杰克·本尼(Jack Benny)、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艾迪·墨菲(Eddie Murphy)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的表演。
如果道德德性是某种从行动中学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得首先养成正当的习惯。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就是法则的首要目的—培养那些形成好品质的习惯。“立法者通过在公民中培养习惯而使他们成为好公民,这是每一个立法者的希冀。那些对这一希冀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法律,就没有达到目标,一个好的宪制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区别于一个坏的宪制。”道德教育并不是在宣传各种规则,而是在培养习惯和塑造品质。“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是否养成这种或那种习惯,不是产生微不足道的差别,而是产生非常重要的差别,抑或是全部的差别。” [256]
亚里士多德对于习惯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认为道德德性是一种机械的行为。习惯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而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习惯最终会起作用,我们也会明白习惯的意义所在。礼仪专栏作家朱迪丝·马丁(Judith Martin)曾经抱怨人们丧失了写感谢信的习惯。她注意到,人们现在认为感觉要胜过礼仪,只要你感到很感激,那么就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些礼节。马丁对此表示反对:“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能更有保障地期望,实践恰当的行为最终能够鼓励有德性的感觉。如果你写了足够多的感谢信,那么你可能最终会感觉到感激之情。” [257]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的看法。专心于有德性的行为,有助于我们获得那种根据德性行动的性情。
人们通常认为,根据德性行动就意味着根据一种戒律或规则而行动。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这种看法丢失了道德德性的一个显著特征。你很可能了解正当的规则而仍然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去应用它。道德教育就在于学着去辨别环境的具体特征,后者要求运用这种而非那种规则。“与行为和什么有益于我们这一疑问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关于健康的问题也同样如此……主体自身必须在每一种情形中去考虑,什么对这一情形来说是恰当的。正如在医学和航行领域所发生的那样。” [258]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关于道德德性,我们所能说的唯一一个一般性的方面就是:它由各种极端之间的中庸所构成。不过他也很乐意承认,这种一般性并不能帮到我们什么,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中辨别出中庸并非易事。其挑战在于:“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分寸上,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动机,以适当的方式”, [259] 做适当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习惯无论有多重要,都不是道德德性的全部。不断会有新的情境出现,而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些情况下,哪一种习惯是恰当的。因此,道德德性就需要判断,这是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智慧”的一门知识。与涉及“普遍的、必要的事物” [260] 的科学知识不同,实践智慧与如何行动有关。它必须“认识到特殊性,因为它是实践性的,而实践与特殊性有关”。 [261] 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界定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真实的、根据人类善而行动的能力”。 [262]
实践智慧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道德德性。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们,不仅能够为自己,也能为同胞和全人类很好地探讨什么是善。探讨并不是哲学化的,因为它关注的是那些多变的、特殊的事物,它所面对的是此时此地的行动。但是它也不止是一种算计,它试图甄别在这些情境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人类善。 [263]
现在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并不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对良善生活来说却必不可少。首先,城邦的法律灌输好习惯、塑造好品质并促使我们形成公民德性。其次,公民生活使我们能够运用慎议和实践智慧的能力,否则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这并不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坐在场外考虑,如果我们需要做出决定的话,自己会支持什么样的政治。可是这不同于参与有意义的行动,并为整个共同体的命运承担责任。只有通过进入场地,权衡各种备选项,争论我们的理由,统治与被统治—简言之,只有成为公民,我们才能善于慎议。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身份与我们的相比要更加崇高、更加热烈。对他而言,政治并不是变相的经济学,其目的要高于使功利最大化,或为追求个体利益提供公平的规则。与此相反,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包括在亚里士多德所赞颂的公民身份当中,妇女不是,奴隶也不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妇女和奴隶的本性并不适合成为公民。我们现在将这种排斥看做一种明显的不公正。值得我们回忆的是,这些不公正在亚里士多德论述之后,持续了两千多年。奴隶制在美国直到1865年才被废除,妇女直到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然而,这些不公正在历史上的持续存在,并不能为亚里士多德接受它们而开脱。
在奴隶制的情形中,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接受了它,而且还为它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论证。他为奴隶制所进行的辩护值得我们检验一番,以便窥斑见豹而弄明白他的整个政治理论。有些人将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论证看做目的论思维的一个瑕疵;而有些人则将其看做这种思维的错误应用,被他那个时代的偏见所蒙蔽。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的辩护,并没有体现出一种非难其整个政治理论的瑕疵。不过,弄明白这种细致深入的主张所具有的力量,也十分重要。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就是一种适合。分配权利也就是为了寻找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他们的、能够使他们实现自己本性的职责。给予人们其应当所得的,就意味着给予他们所应得的职务和荣誉,以及那些与他们的本性相符合的社会职责。
现代政治理论对适合这一观念感到惴惴不安。自由主义的公正理论,从康德到罗尔斯,都担心目的论的观念与自由相冲突。对他们来说,公正与适合无关,而与选择有关。权利的分配并不是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他们本性的职责,而是为了让人们自主地选择他们的职责。
基于这种观点,目的和适合的观念是可疑的,甚至是危险的。由谁来决定什么样的职责适合我,或适合我的本性呢?如果我不能自由地为自己选择社会职责,那么就很可能会违背我的本意而强迫我服从于一种职责。因此,如果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决定某些人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一种从属性的职责的话,那么,适合的观念便很容易滑入奴隶制。
被这种担忧所促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职责应当通过选择,而非适合,来加以分配。我们应当使人们能够为自己选择职责,而不是使人们符合那些我们认为适合于他们本性的职责。以这种观点来看,奴隶制是错误的,因为它强迫人们承担那些他们并没有选择的职责。对此的解决方案就是,反对那种目的论的和适合的伦理,而支持一种选择和同意的伦理。
不过这一结论却过于草率了。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所进行的辩护,并不是一种反对目的论思维的证据。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公正理论,为批判自己在奴隶制上的看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实际上,他的作为符合的公正观念,比那些基于选择和自由的理论,在道德上来说更为苛刻,并且潜在性地对现存的工作分配也更具有批判性。为了弄清楚为何如此,让我们来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论证。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奴隶制要成为公正的,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是必要的;同时,它必须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公民们要花费时间在集会中慎议共同善的话,那么,就必须有人来照顾家庭杂务。城邦需要一种劳动力的划分。除非我们能够发明一些会处理各种卑贱任务的机器,否则,有些人就不得不照料生活必需品,以便他人能够自由地参与政治。
因此,亚里士多德推论说,奴隶制是必要的。不过必要性并不够。奴隶制要成为公正的,就必须也是这样一种情形—有些人出于本性就适合于担任这一职责。 [264] 因此,亚里士多德问道,是否“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而言,奴隶制是更好的、公正的境况?或者其对立面也成立,即:是不是所有的奴隶制都违背本性?” [265] 除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否则政治或经济对奴隶制的需要,都不足以证明奴隶制的公正性。
亚里士多德推论说,这些人是存在的。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他们区别于普通人,正如身体区别于灵魂。这些人“出于本性而为奴隶,并且对他们来说……被一个主人统治更好”。 [266]
“如果一个人能够成为(正因为如此他也确实成为)他人的财产,如果他出于理性而理解了发生于他人身上的事情—唯独不理解他自身,那么这个人在本质上就是一名奴隶。” [267]
“正如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于后者而言,奴隶制的境况不仅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公正的。” [268]
亚里士多德似乎在他所提出的主张中,感觉到了一些令人质疑之处,因为他很快就减弱了语气:“不过,我们也很容易看出,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269] 眼看着他那个时代在雅典所存在的奴隶制,亚里士多德不得不承认,这种批评也有道理。许多奴隶发觉自己是由于一个完全偶然的原因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他们以前是自由人,后来在战争中被俘。他们作为奴隶的状态与他们适合于这一职责无关。对他们而言,奴隶制不是自然的,而是坏运气的结果。借助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标准,他们的奴隶制就是不公正的:“并不是所有的、在现实中是奴隶或自由人的人,其本性上就是奴隶或自由人。” [270]
你怎么能甄别谁适合成为一个奴隶呢?亚里士多德问道。原则上,你可能必须明白,谁(如果有的话)当奴隶的时候比较活跃,谁比较烦躁或试图逃跑。如果需要强迫的话,那么就很好地说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奴隶并不适合于这一职责。 [271]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强迫标志着不公正,这并不是因为同意使所有的职责都合法化,而是因为如果需要强迫,就暗示了一种违背自然的适合。那些担任着一种符合于自己本性的职责的人,并不需要被强制。
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而言,奴隶制之所以不公正,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而对于目的论理论而言,奴隶制之所以不公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本性不一致。强制是不公正的一种症状,而非原因。我们完全能够在目的和适合的伦理中,解释奴隶制的不公正性,亚里士多德给出了某种这样做的方式(尽管不是所有的方式)。
这种目的与适合的伦理,实际上给工作场所中的公正设定了一个道德标准,后者比自由主义的选择和同意的伦理所设定的要更为苛刻。 [272] 让我们来考虑一种重复性的、危险的工作,例如在一个鸡肉加工厂的组装线上长时间地工作。这种形式的劳动是公正的呢,还是不公正的呢?
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工人们是否自由地为了工资而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项工作就是公正的。对于罗尔斯而言,只有当这种劳动力的自由交换,发生于公平的背景条件下时,这种安排才是公正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即使是基于公平的背景条件下的同意,也不够;这项工作要是公正的,它就得符合做这项工作的那些工人的本性。有些工作没有通过这一检验,它们过于危险、重复并使人麻木,因此并不适合于人类。在这些情形当中,公正要求人们重新组织这项工作以符合我们的本性。否则,这项工作就如同奴隶制一样是不公正的。
凯西·马丁(Casey Martin)是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他的一条腿有残疾。由于血液循环系统的紊乱,在比赛场地走动会给马丁造成剧痛,并有大出血和骨折的严重危险。尽管身有残疾,马丁却在这项体育中始终有卓越表现。他上大学时曾在斯坦福的冠军队中打球,后来转为职业运动员。
马丁请求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允许他在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可是PGA援引其禁止在顶级职业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的规定,而拒绝了他。马丁将这一情况上诉至法院,他认为,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只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活动的本质”, [273] 残疾人就有理由要求适当的调整。
一些高尔夫球场上的大腕们在本案中出庭作证。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肯·温图利(Ken Venturi)都不赞成使用球车。他们认为,在高尔夫球联赛中疲劳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开车而不走路,会给马丁带来优势,这对其他人不公平。
案子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发现自己在跟一个似乎很愚蠢的,既低于其尊严又高出其专业知识的问题作斗争:“一个在高尔夫球赛场上坐车从这一挥杆到另一挥杆的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高尔夫球员?” [274]
实际上,这一案例引发了一个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公正问题:为了裁决马丁是否有权使用高尔夫球车,法庭不得不判定所讨论的这一活动的本质。在赛场上走路对高尔夫来说是必不可少呢,还是仅仅出于偶然?如果像PGA所说的那样,走路是这项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那么让马丁坐球车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活动的本质”。为了解决这个与权利有关的问题,该法庭不得不判定这一游戏的目的或本质。
最高法院以7∶2的比例判定,马丁有权利使用高尔夫球车。约翰·保罗·斯蒂文森(John Paul Stevens)代表大多数法官撰写了判决书,分析了高尔夫的历史,并推论说,球车的使用与这一游戏的根本性特征并不矛盾。“最初,这项游戏的本质就是挥杆—以尽可能少的击球次数,用球杆使球从发球区前进至一个洞口的附近。” [275] 针对那种认为走路能检验高尔夫球员的身体耐力的主张,斯蒂文森引用了一位生理学教授的证词。该教授计算了一下,走18个洞口大概只需要耗费500卡路里,“在营养上来说不超过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 [276] 由于高尔夫是一种“低强度的活动,这项游戏所带来的疲劳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其中压力和刺激是关键性的因素”。 [277] 该法庭推断,通过让马丁坐球车而调整他的残疾,并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这项游戏,也不会给他一种不公正的优势。
安东宁·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法官对此表示反对。在一份措辞激烈的反对意见中,他反驳了这样一种观念:法庭可以判定高尔夫运动的本质。他的意思不只是说,法官缺乏权威与能力来裁决这一问题,同时他还质疑那种暗含于最高法院的观点之中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前提,即:我们有可能推理出一项游戏的目的或本质:
说某物是“必不可少的”,在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它对于达到某种目的而言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目的,只有娱乐”(这是游戏与生产活动的区别所在)正是一项游戏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游戏的任何一项任意性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278]
由于高尔夫的各种规则“(如同所有的游戏一样)是完全任意的”,斯卡利亚写道,所以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批判那些由PGA所订立的各种规则。如果球迷们不喜欢它们,“他们可以撤销赞助”。可是没有人会说,这种或那种规则与高尔夫注定要检验的那些技能无关。
斯卡利亚的论点在几个方面是令人质疑的。首先,它贬低了运动。没有一个真正的球迷会这样谈论运动,即:把运动看做完全由任意性的规则所掌控,并且没有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如果人们真的认为,他们最喜爱的运动的规则是任意的,而不是经过策划以激励和赞颂某些令人艳羡的技能和才能,那么他们就很难关心比赛结果。而运动也就会堕落成壮观的场面,成为一种娱乐,而非欣赏的对象。
其次,我们完全有可能讨论不同规则的优劣,并质疑它们是否提升或腐蚀了游戏。这些争论一直在发生—发生于广播的访谈节目中,以及那些掌控游戏规则的人当中。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关于棒球比赛中指定击球员的规则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此规则通过使最佳击球员能够击球,免去对弱投球手的残酷考验,从而提升了该游戏;而其他人则认为,此规则由于过分强调击球,并去除了复杂的策略成分,从而破坏了该游戏。每一种立场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关于棒球到底是什么的观念:它考验什么样的技能,称赞和奖励什么样的才能和德性?因此,关于指定击球员这一规则的争论,最终是关于棒球之目的的争论—正如关于反歧视行动的争论,是关于大学之目的的争论一样。
最后,斯卡利亚通过否认高尔夫具有某种目的,而丢失了该争论体面的一面。这一持续了四年的、关于高尔夫球车的争论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表面上看来,它是关于公平的争论。PGA以及多位高尔夫球名将认为,允许马丁坐车会给他一种不公平的优势;而马丁则回应说,考虑到他的残疾,坐球车只是使比赛场地变平坦一些而已。
如果在这里受到威胁的只是公平,那么,有一种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即:让所有的高尔夫球员在联赛中都使用球车。如果每个人都能坐车,那么这种公平性的反驳便消失了。但是这一解决方案对于职业高尔夫球员来说是极其讨厌的事情,甚至比允许为凯西·马丁破例更加难以想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争论较少涉及公平,更多的是关于荣誉和认可的争论—具体来说,也就是PGA和高尔夫球高手们所期望的—他们的运动被当做一种体育竞赛项目而被认可和尊重。
让我来尽可能细致地阐明这一点:高尔夫球员对于他们的运动状态过于敏感。它没有跑动和跳跃,球也是静止的。没有人质疑高尔夫是一种对技能要求较高的运动;但是,那些奖励给高尔夫球高手们的荣誉和认可,都取决于他们的运动被看做一项对体力要求很高的体育比赛。如果这项他们在其中表现卓越的运动,有人坐在车上就能玩,那么他们作为运动员的认可就会遭到质疑或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职业高尔夫球员强烈反对凯西·马丁使用球车。以下是25岁的美国高尔夫球职业联赛的老手汤姆·凯特(Tom Kit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
在我看来,那些支持凯西·马丁拥有使用球车的权利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在谈论一项具有竞争性的比赛……我们是在谈论一种体育项目。任何认为职业高尔夫不是一项体育运动的人,都没有去过高尔夫球场或没有打过高尔夫。 [279]
不管谁在关于高尔夫的本质问题上是正确的,联邦法庭这个关于凯西·马丁球车的案件,都生动地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争论,经常不可避免地是关于社会制度的目的、社会制度所分配的物品以及它们所尊敬和奖励的德性的争论。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地使法律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中立,可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良善生活的本质,就不可能说明何谓公正。
开口说“对不起”并非易事,可是,代表一个民族在公共场合说抱歉却更困难。近几十年来,人们为是否应该针对历史上的不公正进行公开道歉,而进行了许多痛苦的争论。
许多为道歉感到忧虑的政治观点,都涉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那些历史错误。德国以向个体幸存者赔款和向以色列赔款的形式,为大屠杀做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补偿。 [280] 这些年来,德国的政治领导人都表达了歉意,并不同程度地承担了过去纳粹的责任。在1951年联邦议会上的发言中,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声称:“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憎恨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那些罪恶,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他也承认,“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这么多让人难以启齿的罪恶,这要求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 [281] 2000年,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在以色列的议会上发表演讲,为大屠杀表示道歉,并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 [282]
日本一直不太情愿为其在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暴行道歉。在20世纪30~40年代,成千上万名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和女孩,被迫进入妓院,并被日本士兵当做性奴隶而加以虐待。 [28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就面临日益高涨的国际压力,要求他们向“慰安妇”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私人基金给那些受害者支付赔款,日本领导人也做出了有限的道歉。 [284] 但是,最近在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坚持认为,日本军队并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性奴隶负责。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解决方案做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为此正式道歉。 [285]
其他关于道歉的争论涉及历史上对原住民所作的不公之事。在澳大利亚,近年来人们关于政府对原住民的责任争论不休。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早期,那些混血原住民的子女被迫与他们的母亲分开,并被安置在白人收养家庭或定点营地中。(在大多数这种情况中,孩子们的母亲是原住民,而父亲是白人。)这项政策试图使孩子们融入白人社会,并加速土著文化的消亡。 [286] 电影《末路小狂花》(Rabbit-Proof Fence)刻画了这种政府支持的绑架。该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1年,三个女孩从一个定点营地逃跑,踏上长达1 200英里的、返乡寻母的旅途。
1977年,一个澳大利亚的人权委员会为发生在“被偷的一代”的原住民身上的那些残忍事件提供了文件证明,并提议将每年的某一天作为全国道歉日。 [287] 当时的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反对正式道歉,于是这一道歉问题成为澳大利亚政坛上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事件。2008年,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对原住民发表了一份官方道歉。尽管他没有提出要对个体进行赔偿,但是他承诺,将使用多种手段来克服原住民所遭受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不便。 [288]
在美国,近几十年来,关于公开道歉和补偿的争论也日益凸显。1988年,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生效了一份官方致歉,向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监禁在西海岸拘留营中的美国籍日本人道歉。 [289] 除了道歉,这项法律还向从拘留营中存活下来的每个人提供两万美元的补偿,并提供基金支持以促进美籍日本人的文化和历史发展。1993年,国会为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错误道歉—为一个世纪以前推翻独立的夏威夷王国而道歉。 [290]
在美国,最严重的道歉问题与奴隶制的遗留问题有关。内战对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所承诺的“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子”从来都没有兑现过。20世纪90年代,补偿黑人的运动获得了新的关注。 [291] 从1989年开始,国会议员约翰·克尼尔斯(John Conyers)每年都会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补偿问题。 [292] 尽管这种补偿的想法得到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组织以及民权团体的支持,但是它并没有在普通公众中流行起来。 [293] 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补偿,而支持补偿的白人则只有4%。 [294]
尽管补偿运动可能已经中止,可是近些年却掀起了正式道歉的浪潮。2007年,曾经是最大蓄奴州的弗吉尼亚州,第一个为奴隶制而道歉。 [295] 许多其他的州,包括亚拉巴马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以及佛罗里达州,都相继效仿。 [296] 2008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歧视黑人时代(Jim Crow era)的种族隔离而道歉。 [297]
国家应当为历史上的过错道歉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关于集体责任和共同体的主张的棘手问题。
对公众道歉所进行的主要辩护是—为了尊重一些人们的记忆,他们曾遭受过那种来自于政治共同体(或以政治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不公正;为了认识到不公正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持续性影响;还为了偿还那些行不义之事的、或没有阻止不义之事的人们所犯下的过错。官方道歉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能够有助于愈合以往的伤口,并为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和解提供一个基础。补偿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赔偿,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得到辩护,它们也能有助于缓解那些不义行为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影响。
这些考虑是否足够强烈地证明一个道歉是正当的,这取决于具体情境。在某些情况中,促成公开道歉或补偿有可能弊大于利—煽动过往的仇恨,强化历史的恩怨,巩固一种受害感或产生憎恨。反对公开道歉的人经常表达出类似的担忧。如果考虑周全的话,一种道歉或补偿行为是更可能治愈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更可能毁坏一个政治共同体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判断。而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因具体情形而异。
我想集中关注另一个经常由反对为历史上的不公正道歉的人所提出的论点—原则性的、并不依赖于具体情境之偶然性的论点。该论点是:当代的人们不应当—实际上也不能—为前辈们所犯的过错道歉。 [298] 毕竟,为一种不公正道歉,就是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你不能为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道歉,因此,你如何能够为那些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道歉呢?
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用这一论点来反对向原住民正式道歉:“我并不认为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应当为前一辈人的行为正式道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99]
在美国关于奴隶制补偿问题的争论中,也产生了类似的论点。亨利·海德(Henry Hyde)是一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他基于以下几种理由而反对这种补偿观念:“我从未拥有过奴隶,也从来没有压迫过任何人。我不知道自己还得为在我出生几代之前曾经拥有过奴隶的那些人还债。” [300] 反对补偿的非洲裔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如果政府能从圣诞老人或牙仙 (11) 那里获得这笔钱的话,那还可以;可是政府却不得不从公民那里获得这笔钱,并且那些对奴隶制负有责任的公民都已经驾鹤西去了。” [301]
向当今的公民征税以补偿过往的错误,这似乎会引发一个特殊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涉及经济补偿的、关于道歉的争论当中,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在道歉当中,起作用的是思想;这里受到威胁的思想是承认责任。任何人都能遣责不公正的行为,但只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牵涉这一不公正的人,才能为之道歉。道歉的批评者们正确地抓住了这里的道德风险,他们还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当代人在道德上能够对他们的前辈所犯下的过错负责。
2008年,当新泽西州立法委员会为道歉问题争论的时候,一名共和党的议员问道:“有哪个活着的人因蓄奴而有罪,并因此能够为此道歉?”在他看来,答案很明显—没有人。“新泽西州现在的居民,即使是那些能够追溯到祖先是蓄奴者的人们,对那些他们个人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不公正的行为,都不负有任何集体性的罪恶感或责任。” [302]
当美国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是否要为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而道歉时,一位反对这种方式的共和党人,将这种行为比做“为你的曾曾曾祖父的行为而道歉”。 [303]
这种对官方道歉的原则性的反对,并不容易被驳倒。它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只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他人的行为,或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件负责。我们对自己父母、祖父母以及同胞的罪行,并没有责任。
不过这就将这一问题负面化了。这种对官方道歉的原则性的反对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援引了一种强有力的、有吸引力的道德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观念称为“道德个人主义”。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学说,并不假设人们是自私的;相反,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意味着自由”的主张。对于道德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就意味着仅仅从属于那些我所自愿承担的责任;我所亏欠别人的任何东西,都是出于某种同意的行为—我所做出一个选择、一个承诺,或我所签订的某个协议(无论它是心照不宣的还是明确表达的)—而亏欠。
“我的责任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担的”这一观念,是一个具有解放性意味的观念。它假设:作为道德主体的我们,是自由而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先在的道德纽带的约束,能够自主地为自己选择各种目的;那唯一约束我们的道德责任的来源,并不是习俗、传统或继承状态,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
现在你能够明白,这种自由观给集体责任,或那种承担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所做的不公正行为的道德责任的义务,留下了极少的余地。如果我对祖父做出承诺说会偿还他的债务,或为他的罪行道歉,那将会是一回事。我完成偿还的义务,将是一种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的义务,而并不是从那种跨越几代人的集体身份所产生的义务。没有这些承诺,道德个人主义者就不能明白那种为祖先的罪恶赎罪的义务。毕竟,这些罪恶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如果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是正确的,那么那种对官方道歉的批评之声就有可取之处,我们对祖先的过错并没有任何责任。可是,不只是道歉和集体责任处于危险的境地。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观,体现于当代政治领域中最为人熟知的诸多公正理论当中。如果这种自由观是有缺陷的—正如我所认为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公共生活的一些根本性特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意和自由选择的观念,不仅在当代政治领域十分突出,在现代公正理论中也非常突出。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并弄明白各种各样的关于选择和同意的观念,是如何影响我们当代的各种假设的。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较早版本的、选择性的自我,来自于约翰·洛克。他认为,合法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独立的存在,并不受制于家长式的权威或国王的神圣权利。由于我们“在本性上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因此就没有什么能不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而使他们脱离于这种状况,并受制于另一种政治权力”。 [304]
一个世纪以后,伊曼纽尔·康德提出了一种更有力的、选择性的自我。与功利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们相反,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将自己看做超越于各种偏好和欲望。要成为自由的,就是要成为意志自由的;而要成为意志自由的,就是要受制于我给自己所定的法律。康德式的意志自由比同意更为苛刻。当我命令该道德法则时,我不是仅根据我的偶然性的欲望或忠诚而选择;相反,我远离于我的各种特殊的利益和情感,而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参与者来命令。
到了20世纪,约翰·罗尔斯沿用了康德的意志自由的自我观,并将它运用到自己的公正理论当中。和康德一样,罗尔斯注意到,我们所做出的选择经常反映出道德上的任意偶然性。例如,某个人之所以选择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可能反映出他急需要钱,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成为一种自愿的安排,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它建立在实际的同意之上;相反,我们应当疑问,如果我们搁置自己各种特殊的利益和优势,而在无知之幕的背后做出选择的话,我们会同意什么样的公正原则。
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和罗尔斯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假想的契约观念,在以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两者都将道德主体看做独立于自身的各种特殊目的和情感。在命令道德法则(如康德)或选择公正原则(如罗尔斯)的时候,我们并不带有那些使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并使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角色和身份。
如果我们在思考公正的时候,必须从我们的各种特殊身份中抽离出来,那么就很难说,当代的德国人肩负着一种弥补大屠杀的特殊责任;也很难说这一代的美国人,肩负着纠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之不公正的特殊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搁置了我作为德国人或美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并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那么就没有理由说,我纠正这些历史性的不公正的责任,要比别人更大。
将人们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仅使代与代之间的集体责任问题有所不同,它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含义: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道德主体,会给我们更为一般性地思考公正问题的方式带来影响。“我们是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的这一观念,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公正原则,不应当建立在任何一种特殊的道德和宗教的观念之上;相反,它们应当中立于各种不同的良善生活观。
“政府应当试图中立于良善生活的意义”这一观念,体现出一种对古代政治观念的背离。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疏通经济贸易,提供共同防御,它还为了培养良好品质和塑造好公民。因此,关于公正的争论,就不可避免地是关于良善生活的争论。“在能够研究一种理想宪制的本性之前,”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有必要首先决定那种最佳生活方式的本性。只要这一点是模糊的,那么理想宪制的本性就肯定也是模糊不清的。” [305]
如今,“政治就是培养德性”这一观念作为一种奇怪的,甚至是危险的观念,使很多人感到震惊。由谁来决定要包括什么样的德性呢?如果人们不同意怎么办呢?如果法律试图推进某种道德和宗教理想,这不是给不宽容和强迫开了方便之门吗?当我们想到那些试图推进德性的国家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雅典式的城邦,而是过去和现在的宗教激进主义—例如对通奸者施以石刑、强迫妇女身着长袍以及对“塞勒姆女巫”的审判 (12) 等等。
对于康德和罗尔斯而言,基于某种良善生活观念的公正理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与自由相冲突。由于将某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这些理论都没有将人们尊重为自由的、独立的、能够选择自己的意图和目的的自我。因此,这种自由选择的自我与中立型政府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我们是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拒绝在各种道德和宗教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的,并且让公民们自由选择各种价值观的权利框架。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没有哪一种公正和权利理论能够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在一个层面上,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康德和罗尔斯都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人们应当自由选择自己的目的”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观念。不过,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去生活,而只是要求: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你追求的方式都应该尊重他人也这样做的权利。一个中立性框架的吸引力正在于,它拒绝去肯定一种更为可取的生活方式和良善观念。
康德和罗尔斯并不否认,他们是在推进某种道德理想;他们是在与那些从某种善观念中推论出权利的公正理论作斗争。功利主义就是一种这样的理论。它认为,善就在于使快乐或福利最大化,并追问什么样的权利体系可能实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善的理论。它并不在于使快乐最大化,而在于实现我们的本性,发展我们独特的人类能力。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是目的论的,因为他是从一种特定的、关于人类善的观念开始推理。
这种推理模式正是康德和罗尔斯所反对的。他们认为,权利优先于善。那些将我们的义务和权利具体化的原则,不应当建立在任何特殊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之上。康德写到了“哲学家们对道德最高原则的混淆”。古代的哲学家们犯了这样的错—“将他们的伦理研究完全投入对最高善观念的定义”,并接着使这种善成为“道德法则的决定性基础”。 [306] 但是,根据康德的观点,这样就本末倒置了,而且也与自由相冲突。如果我们要将自己看做意志自由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命令道德法则。只有当我们达到了那界定我们各种义务和权利的原则之后,我们才能询问,什么样的善观念能与之兼容。
罗尔斯本着对公正原则的尊敬而做出了与康德类似的论断:“当平等公民身份的各种自由,建立在目的论原则之上时,这些自由就是不可靠的。” [307] 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将权利建立在功利主义的思考之上,会怎样使权利不牢靠。如果人们尊重我的宗教自由权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促进总体的善,那么,如果某一天大多数人鄙视我的宗教并想要禁止它,该怎么办?
但是,功利主义的公正理论并不是罗尔斯和康德的唯一批判目标。如果权利优先于善,那么亚里士多德思考公正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推理公正就是从所讨论的事物的目的或本性来推理;要思考一种正当的政治秩序,我们就不得不从良善生活的本性来进行推理。我们只有首先弄明白最佳的生活方式,然后才能构建起一个公正的宪制。罗尔斯对此表示反对:“目的论学说的结构完全是一种误解:从一开始它们就将权利与善以错误的方式连接起来。我们不应当试图首先依靠那被独立界定的善,而规划我们的生活。” [308]
在这一争论中岌岌可危的不只是那个抽象的“我们应当怎样推理公正”的问题。这个关于权利对善的优先性的争论,最终是一个关于人类自由的意义的争论。康德和罗尔斯之所以反驳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因为它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余地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善。我们很容易弄明白,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如何引起这种担忧的:他将公正看做人们和那些适合于他们本性的各种目的或善之间的适合。可是,我们倾向于将公正看做一种选择,而非适合。
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的理由,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拥有他所选择的各种目的的主体。” [309] 作为道德主体,我们并非由自己的目的所界定,而是由自己的选择能力所界定。“主要揭示我们本性的,并不是我们的各种目标”,而是那种如果我们能够抽离于自己的各种目的就会选择的权利框架。“由于自我优先于那些由它来认定的目的,因此,即使是一种主导性的目的,也必须从多种可能性中被选择出来……因此,我们应当将目的论学说所提出的权利与善之间的关系反转过来,而将权利看做先在的。” [310]
“公正应当中立于各种良善生活观念”这一观点,反映出一种人的观念,它将人看做自由选择的自我,不受任何先在的道德约束。这些观念放在一起,就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特征。我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的那个概念,因为这些术语被应用于美国政治争论当中。实际上,美国政治争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们能够在政治领域当中,发现那种中立型政府和自由选择性的自我理想。许多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争论,就是关于如何最好地使个体自主地追求自己目的的争论。
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支持公民自由以及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医疗权利、教育权利、工作权利、收入保障权利,等等。他们认为,要使个体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就需要政府能够保障真正自由选择所需要的那些物质条件。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福利国家的倡导者们,就很少以社会团结和相互责任的名义,而更多地以个体权利和自由选择的名义进行论证。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5年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时,他并没有表明该制度表达了公民间的相互责任;与之相反,他将它设计成一种与私人保险相类似的、由薪水供款而非一般性税收所资助的方案。 [311] 1944年,在筹划一项美国福利国家的议程时,他称之为“经济权利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提出一种公共性的理由,与此相反,他认为,这些权利对“真正的个体自由”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并补充道:“处于贫困境地的人,并不是自由的人。” [312]
从他们这一方来看,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在当代政治领域中,至少是在经济问题上,他们通常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也呼吁一种尊重个人选择的中立型政府。(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写道,政府必须“在其公民中间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 [313] )不过,他们不同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在“这些理想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批评福利国家而支持政府放任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们,维护自由市场,并认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所赚的钱。巴里·戈登瓦特(Barry Goldwater)是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一名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质问道:“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果实不能任由自己支配,而是被当做共同财富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怎么能是真正自由的呢?” [314] 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们而言,一个中立型的政府需要公民自由以及严格的私有财产权制度。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并不能使个体选择自己的目的,但却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去强迫另一些人。
无论是平等主义者还是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些追求中立性的公正理论都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吸引力。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希冀:政治和法律能够避免陷入那充斥于多元主义社会的、各种道德和宗教的争论之中。它们也表达了一种令人兴奋的人类自由观—它将我们看做唯一束缚我们的道德责任的创立者。
然而,尽管这种自由观具有吸引力,但它却是有缺陷的。那种试图找到能中立于各种不同良善生活观念的公正原则的期望,也是有缺陷的。
这至少是我从其中得出的结论。在与这些我置于你们面前的各种哲学争论较量之后,在关注这些争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展开方式之后,我认为自由选择—即使是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并不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充分基础。再者,那种试图找到中立性的公正原则的尝试,在我看来也具有误导性。我们不可能总是不涉及重大的道德问题,而界定我们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值得欲求的。我将试着来解释原因。
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薄弱之处,与它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我们通常认可甚至奖励的道德和政治义务。这包括团结和忠诚的义务、历史性的记忆和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些产生于塑造我们身份的、共同体的和传统的道德主张。除非我们将自己看做受约束的自我,对一些我们并不想要的道德主张开放,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和政治经验中的这些方面。
20世纪80年代,在罗尔斯的《正义论》给美国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最详尽的哲学表达10年之后,许多批评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依据我刚刚所表明的,对这种自由选择、无约束的自我观念提出了质疑。他们反对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并且认为,我们不能抽离于自己的各种目标和情感而推理公正。他们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主义”的批评者而闻名于世。
大多数批评者对这一标签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它似乎暗示了那种相对主义的观点—公正不过是任何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所界定的那样。但是,这种担忧却提出了重要的一点:那种公共性的束缚可能具有压迫性。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作为一种对某些政治理论的纠正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政治理论将人交付给那受种姓、阶层、身份、登记、习俗、传统或继承身份等决定的命运。因此,我们怎么才能既承认共同体的道德分量,同时又给人类自由留有余地呢?如果说意志论关于人的观念过于狭隘—如果我们所有的义务都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将自己看做情境的,而且是自由的呢?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回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After Virtue)中,他说明了作为道德主体的我们达到自身意图和目的的方式。作为意志论的人格观念的一种替代物,麦金泰尔提出了一种叙述性的观念。人类是讲故事的存在,我们作为叙述性的探求者而生活着。“如果我能回答一个先在的问题—‘我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故事之中?’那么,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 [315]
麦金泰尔论述道,所有作为叙述者而存在的人,都有某种目的论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一个由外在权威所设定的、固有的意图或目的。目的论与不可预测性同时共存。“像那些在叙述性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们的生活依然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这种形式自身朝着我们的将来而做出谋划。” [316]
过一种生活就是制定一种叙述性的探求,它追求某种功利或连贯性。当我们面临不同的选择道路时,我会试图弄明白,哪一条道路能最好地理解我的整个生活,理解我所关心的各种事物。道德慎议更多的是阐释我的生活故事,而并不只是运用我的意志。它涉及选择,可是这种选择源自于阐释,它并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意志行为。在任何时候,他人都可能会比我更加清楚地明白,在我眼前的各种道路中,哪一条道路更加符合我的生命轨迹。我经过考虑,可能会说,我的朋友比我更加了解自己。对道德主体的这种叙述性的长处就在于,它能够给这种可能性留有余地。
它也说明了道德慎议是如何在那种更宏大的生活故事中反思以及反思这种更宏大的生活故事本身的—我的生活是这种宏大的生活故事的一部分。正如麦金泰尔所言:“我永远也不能仅仅通过个人来寻求善和运用各种德性。” [317] 我只有通过进入我自身所处的那些故事,才能理解那种对我的生活的叙述。对于麦金泰尔(以及亚里士多德)而言,道德反思的这种叙述性的、目的论的方面,与成员身份和归属感紧密相关。
我们都是作为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进入自己的各种环境。我是某人的儿子或女儿、表兄妹或叔叔;我是这个或那个城市的公民,是这个行业或那个职业的成员;我属于这个家族、那个部落或这个民族。因此,那些对我有益的,也得对担任这些角色的人同样有益。同样的,我从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和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遗产、正当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我生活中的特定成分和我的道德起点。这部分地给予了我自己的生活以道德独特性。 [318]
麦金泰尔很乐意承认,这种叙事性的说明与道德个人主义相冲突。“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而言,我是我自己选择成为的那个人。”在个人主义者们看来,道德反思要求我搁置或抽离于我的身份和束缚:“人们不能认为我对国家的所作所为,或已经做出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我暗示性地或明确地选择去承担这样的责任。这种个人主义由现代的一些美国人所表达,他们拒绝对奴隶制给美国黑人所带来的影响承担任何责任,并扬言‘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奴隶’。” [319] (我们应当注意,麦金泰尔大约在国会议员亨利·海德反对补偿时明确地表达这一点的20年前,就已经写下了这些文字。)
麦金泰尔还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例子:“一些年轻的德国人相信,在1945年后出生就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与他和同辈犹太人的关系,没有任何道德关联。”麦金泰尔在这种观点中看到了一种道德上的肤浅。它错误地假设:“自我脱离于其社会的和历史的角色和状态。” [320]
它与叙述性的自我观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因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割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 [321]
麦金泰尔的叙述性的人的观念,与意志论的“作为自由选择的、无约束的自我”的人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两者之间如何裁决呢?我们可能会扪心自问,哪一种更好地捕捉了道德慎议的经历,但这是一个难以抽象地回答的问题。另一种评价这两种观点的方式就是询问,哪一种为道德和政治义务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是不是与某些未经选择的、无法追溯到某个社会契约的道德纽带紧密相关呢?
罗尔斯的回答将是否定的。在自由主义的观念当中,义务只能产生于两种方式—我们对人类负有的一些自然的责任,以及出于我们的同意而产生的自愿的责任。 [322] 自然的责任是普遍性的。我们作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而负有这些责任。它们包括尊敬地对待他人的义务、做公正之事的义务、避免残忍的义务,等等。由于它们产生于一种意志自由(康德)或一种假想的社会契约(罗尔斯),因此它们并不需要同意。没有人会说,只有当我向你承诺过不杀你,我才有义务不杀你。
与自然的义务不同,自愿的义务是特殊的,而并非普遍的,并且产生于同意。如果我已经同意去给你的房子刷漆(如为了换取工资或为了报答你曾给我的帮助),那么我就有义务这样去做。不过我并没有义务去给每个人的房子刷漆。基于自由主义的观念,我们必须尊重所有人的尊严;但是,越过这一层面,我们仅仅亏欠那些我们所同意亏欠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公正要求我们尊重人们的权利(由中立性的框架所界定的权利),而不要求我们促进他们的善。我们是否必须关心他人的善,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与谁已经达成了协议去这样做。
这种观点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含义就是:“严格说来,公民们一般没有政治义务。”尽管那些竞选公职的人自愿地承担一种政治义务(也就是,如果被选上的话就要为国效力),而普通公民则无须如此。正如罗尔斯所写的:“我们并不清楚那必不可少的、应该履行的行为是什么,或是谁履行了它。” [323] 因此,如果自由主义关于义务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一般公民对其同胞们,就没有那种超越于普遍的、自然的不作恶之义务的特殊义务。
从叙述性的关于人的观念来看,自由主义关于义务的论证过于浅薄。它没有说明我们作为公民而对同胞所具有的特殊义务;再者,它没有捕捉到那些忠诚和责任—它们的道德力量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依靠它们而生存,与将我们理解为已然所是的特殊的人—作为这个家庭、国家或民族的成员,作为那种历史的承担者,作为这一共和国的公民—不可分割。基于这种叙述性的论证,这些身份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当我们慎议道德和公正时应当搁置的,它们就是我们所是的一部分,并因此正当地与我们的道德责任有关。
因此,在唯意志论的人的观念和叙述性的人的观念之间,做出裁决的一种方式就是:询问自己是否认为有第三种不能在契约论术语中得到解释的义务—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成员的义务。与自然的义务不同,团结的义务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们涉及一些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共享某种历史的人—而非理性存在,所亏欠的道德责任。但是与自愿的义务不同,团结义务并不取决于同意的行为。与之相反,它们的道德力度源于道德反思的情境性的方面,源自于这样一种认知:我的生活故事暗含于他人的故事之中。
三种道德责任:
1. 自然的义务:普遍的;不需要同意
2. 自愿的义务:特殊的;需要同意
3. 团结的义务:特殊的;不需要同意
以下是一些团结或成员的义务的可能性事例。看看你是否认为它们具有道德分量,如果有的话,它们的道德力量是否能够用契约式的术语来加以说明。
最基础性的事例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义务。假设有两个孩子快要被淹死了,而你只有时间救上来一个。一个是你自己的孩子,而另一个是陌生人的孩子。你救自己的孩子有错吗?抛硬币来决定是不是更好呢?大多数人会说,救自己孩子并没有什么错;他们也会认为,“公平要求抛硬币来决定”的想法十分怪异。在这种反应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思想: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幸福,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有些人认为这种责任源自于同意。通过选择生育孩子,父母们便自愿地同意去特殊地照顾他们。
让我们将同意搁置一旁,而考虑孩子对父母的责任。假设有两名老人需要照顾,一位是我的母亲,而另一位是别人的母亲。大多数人会同意说,如果我能照顾两位,那将是令人称赞的;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照看自己母亲的责任。在这一情形当中我们不清楚,同意能否解释为何如此。我并没有选择我的父母,我甚至没有选择要拥有父母。
可能有人会争论说,我照顾自己母亲的道德责任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在我很小的时候照顾了我。由于她抚养了我、照顾了我,所以我有义务偿还这一好处。由于接受了她给我带来的好处,我就心照不宣地同意,当她需要的时候就去偿还她。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这种关于同意和互惠的算计,过于冷漠而无法解释家庭责任。但是,假设你接受了它,你会怎样评价其父母疏忽大意或冷漠无情呢?你能说,抚养子女的好坏,决定了子女在父母需要帮助时所负责任的多少吗?就孩子们有义务去赡养哪怕是有劣迹的父母而言,这种道德主张可能超越了互惠和同意的自由主义伦理。
让我们从家庭转移至集体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对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轰炸。尽管他们的目标是工厂和其他军事目标,可是他们并不能避免平民的伤亡。有一天,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接到命令后发现,他的轰炸目标是他家所在的村庄。(这个故事可能不足为信,但是它却引发了一个引人关注的道德问题。)他请求将自己排除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外。他承认,轰炸这个村庄与他昨天执行的任务,对于达到解放法国的目标来说同样必要;并且他知道,如果他不执行,其他人也会执行。但是他基于这样的理由而迟疑:他不能成为那个轰炸自己家乡并可能炸死一些他的乡亲的人。他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正当的情境中,由他来执行这次轰炸,也将是一个特殊的道德错误。
你如何理解这名飞行员的看法呢?你是敬佩这种看法还是认为它是一种软弱?让我们搁置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在解放法国的情形中,多少平民伤亡是正当的。这名飞行员并不是在质疑这次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或将要损失多少生命,他的要点在于,他不能成为那个夺去这些特殊生命的人。这名飞行员的不情愿是过分的拘谨呢,还是反映出某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敬佩这名飞行员,那么肯定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观点中看到他认同了自己作为村庄成员的这种受约束的身份,我们敬佩他的不情愿所反映出来的品质。
20世纪8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的一场饥荒迫使大约40万难民涌入邻国苏丹,他们在那里的难民营中饱受困苦。1984年,以色列政府发起了一项称为“摩西行动”(Operation Moses)的空运转移,以解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亦即法拉沙人,并将他们带到以色列。 [324] 在阿拉伯国家对苏丹施压、要求它不要配合以色列的撤离行动之后,这项行动停止了,大约有7 000名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获救。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说道:“直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从埃塞俄比亚安全地回到家中,我们才会停下来。” [325] 1991年,当内战和饥荒威胁到余下的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时,以色列执行了一次更大的空运,将1.4万名法拉沙人带到了以色列。 [326]
以色列拯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的行为,是否是一种正当行为呢?我们很难不将这种空运看做英勇的行为。那些法拉沙人当时处于绝望的境况之中,他们希望能够回到以色列。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之后建立的犹太人国家,它的建立就是为了给犹太人提供一个家乡。但是让我们来假设有人提出了以下这种质疑:有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难民正遭受饥荒,假设考虑到有限的资源,以色列只能救走一小部分人,为什么它不应当抽签决定拯救哪7 000名埃塞俄比亚人呢?只空运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而非一般的埃塞俄比亚人,为什么这不是一种不公平的歧视呢?
如果你接受了团结和归属的义务,那么该问题的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拥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来援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这超越它(以及所有国家)帮助一般难民的义务。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尊重人权,这要求它根据自己的能力,给那些在任何地方正遭受饥荒、迫害或背井离乡的人们提供帮助。这是一种能够根据康德式的理由而得到辩护的普遍义务,是我们作为人、作为人类同胞而对他人具有的义务(义务种类一)。我们这里试图裁决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具有更进一步的、特殊的义务来关心它们的人民。通过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称为“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位以色列总理援引了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团结的隐喻。除非你接受这种观念,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不应该通过抽签来实施空运救援,你也有可能很难去维护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备受争议的道德情感。有些人将爱国看做一种不容置疑的美德,而另一些人则将它看做无知服从、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源头。我们的问题则更为特殊:公民们相互间是否具有一些义务,这些义务超越了那种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的义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义务能否仅仅基于同意而得到解释?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爱国主义坚定的维护者,他认为,这种集体的情感和身份是对我们普遍人性的必要补充。“似乎人类的情感在被延展至整个世界时,便蒸发了或变弱了;似乎鞑靼地区或日本的灾难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像欧洲人的灾难对我们的影响一样。利益和同情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约束而不起作用。”他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限制性的原则,它增强了同胞们的感情。“这是一件好事:那集中于公民同胞之间的人性,通过相互探望对方的习惯和那种使它们联合起来的利益,而呈现出新的力量。” [327] 但是,如果公民同胞们被忠诚和共性绑在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相互间所亏欠的要比亏欠他人的多。
我们希望人们成为有德性的吗?那么,我们首先要让他们爱国。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对他们与对外国人一样,只分配给他们那些和外国人的份额一样的东西,那么他们又怎么能爱这个国家呢? [328]
国家确实要给自己的人民比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东西。如美国公民就有资格享有多种形式的公共设施—公共教育、失业补偿、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医疗、福利、食品券等等—而外国人则没有资格享受这些。事实上,那些反对更宽松的移民政策的人们,就是担心这些新的加入者会分享那些美国纳税人所支付的社会项目。但是,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对自己那些需要帮助的公民所负的责任,要大于他们对住在其他地方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公民所负的责任?
有些人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众补助,而想要按比例缩减国家福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在给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供国际援助时,应当比现在更加慷慨。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福利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区别;而且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义务来满足自己公民的需求,而这种义务并不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种区别在道德上是可辩护的吗,还是它仅仅是一种对自己人的偏袒和偏见?国家边境的道德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完全从需要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近10亿每日消费不到1美元的人,比我们国家的穷人状况更糟糕。
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Laredo)与墨西哥的华雷斯(Juarez)是两个相邻的小镇,由格兰德河(Rio Grande)隔开。一个出生于拉雷多的孩子有资格享有美国福利国家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并且长大后,他有权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工作。而出生在河对岸的孩子则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权利越过这条河。尽管这些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可是两个孩子仅仅由于出生地的缘故,而将会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前景。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国家共同体的理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拥有对等的财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公民,那么,特殊照顾自己人民的那种义务就不会有问题—至少从公正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可是,在一个贫国和富国之间差距巨大的世界当中,共同体的主张可能会与平等的主张形成张力。那反复无常的移民事件就反映出这种张力。
移民政策改革是一个政治雷区。那唯一赢得广泛的政治上支持的移民政策内容,就在于其决心巩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安全,以限制非法移民的潮流。得克萨斯的县治安官最近发明了一种新颖的使用网络来帮助他们看守边境的方法。他们在那些广为人知的非法入境地区安装了摄像头,并将来自摄像头的实时录像放在一个网站上。那些想要帮助监视边境的公民们,可以在网上当“事实上的得克萨斯警官”。如果他们看到有人企图穿越边境,就给县治安官的办公室发送一份报告,有时候该办公室会在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帮助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当我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上听到这个网址时,我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促使那些人坐在电脑屏幕前盯着。这肯定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工作,长时间不活动,还没有报酬。记者采访了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名卡车司机,他是成千上万个登录那个网站的人之一。在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这个卡车司机“回到家中,将自己6英尺高、6英寸宽、250磅的身躯置于电脑面前,打开一罐红牛……然后开始保卫他的祖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记者问道。“这给我一种优越感,”卡车司机回答道,“就像我在为执法部门和我们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329]
这可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怪异的表达方式,但是它却引发了一个移民争论的核心问题: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国家阻止外人进入其疆域是正当的?
限制移民的最佳理由是一个集体的理由。正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写的,管理公民身份条件的能力,设定准入和排外的这种能力,是“集体独立性的核心所在”。否则“那些共同体的特质,以及人们带着彼此间的特殊承诺和对集体生活的某种特殊情感而成立的各种协会,就不会具有历史的稳定性”。 [330]
然而,对于富国而言,限制移民政策同样也是为了保护特权。许多美国人害怕,大量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后会对社会服务产生巨大负担,也会降低现有公民的经济利益。我们不清楚这种担心是否正当,但是,让我们为了论证而假设:开放移民政策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标准。这是限制移民的足够的理由吗?除非你认为,那些在格兰德河富裕的河岸出生的人,有资格享有他们的好运气。然而,由于出生的偶然性并不是资格的基础,所以我们很难看清,限制移民的政策如何能够以维持富裕的名义而得到辩护。
限制移民的一个更强的论证就是保护低技能的美国人的工作和工资水平,他们最容易被大量涌入的那些愿意为较少工资而工作的移民所取代。但是,这种理由将我们带回至我们正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如果保护我们那些最脆弱的工人,就意味着不给那些来自于墨西哥的更贫穷的人们工作机会,那么我们为什么应当保护他们呢?
从帮助最不利者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支持开放移民的理由。但是,即使是带有平等主义同情的人们,也不情愿接受它。 [331] 这种不情愿是否有一种道德基础呢?是的,但是只有当你接受以下这一点时,答案才是肯定的:由于公共生活和共同分享的历史,我们对同胞公民们的幸福肩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而这也依赖于我们接受那种叙述性的人格观念,根据这种人格观念,我们作为道德主体的身份与我们所居住的共同体紧密相关。正如沃尔泽所写的:“只有当爱国情感具有道德基础时,只有当集体的凝聚力促进了责任和共享的意义时,只有当既有成员又有陌生人时,政府官员才有理由特别担心自己人民的幸福……以及自己文化和政治的成就。” [332]
移民并不是美国的工作会丢失给外人的唯一途径。如今,资本和商品比人更加容易穿越国家边境,这也引发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道德状态的问题。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广为人知的口号—“购买美国货”。买福特汽车而不买丰田汽车是不是一种爱国呢?随着汽车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供应线而生产出来,我们更难明确地知道,什么才算做一辆美国制造的汽车。但是,让我们假设自己能够甄别出那些给美国人带来工作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好的购买它的理由吗?为什么我们应当对给美国工人—而不是日本的、印度的或中国的工人—创造工作机会更感兴趣呢?
2009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该法律包括一项要求,即:由该法案资助的公共工作—如道路、桥梁、学校以及公共建设等—都要使用美国制造的钢铁。“这只是说明了,我们可能刺激我们自己经济的哪一个方面,而不是别的国家的经济。”参议员拜伦·多尔根(Byron Dorgan)是一个“购买美国货”规定的支持者 [333] ,他如此解释道。这一规定的反对者们害怕它会促进别的国家报复美国的商品,从而加剧经济的下滑,并最终导致美国工作的丧失。 [334] 但是没有人会质疑这样一种设想,即:这一刺激计划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创造就业机会。这一设想生动地体现于一个术语当中,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渗漏”一词来描述一种危险:美国的政府支出会资助国外的工作。《商业周刊》的一则封面故事就聚焦于这一渗漏问题:“奥巴马的巨大的经济刺激会有多少渗漏至国外,而在中国、德国或墨西哥比在美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 [335]
在每个地方的工人们都面临着失业时,我们能够理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将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当做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渗漏的言论将我们带回至爱国主义的道德状态。如果仅仅从需要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呼吁人们去帮助那些失业的美国工人,而不是中国的失业者。但是却很少有人反对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去帮助自己的同胞们。
我们很难从同意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义务。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要帮助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工人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工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已经隐而不宣地同意了;由于我从一个国家经济所体现的相互依赖的复杂计划中受益,我就对这种经济的其他参与者负有一种互惠的义务—尽管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们,尽管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跟他们的大多数人交换过任何商品和服务。但是这是一种歪曲。如果我们试着去追溯当代世界中那广泛分布的经济交换的关节点时,我们就很可能会发现,我们对那些居住在半个世界之外的人非常依赖,就像我们那样依赖印第安纳州的人一样。
因此,如果你相信爱国主义具有一个道德基础,如果你相信我们对自己同胞们的幸福具有特殊的责任,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第三种义务—那不能被归纳为一种同意的行为的团结或成员的义务。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同事和同胞具有特殊的责任。有些人认为,所谓团结的义务实际上不过是集体自私的范例,是对自己人的一种偏袒。这种批评承认我们一般比关心他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但是,他们质问道:“难道这种对自己人的更多关心,不是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趋势,而是以爱国主义或兄弟会的名义加以维持的、目光狭隘的、越来越封闭的趋势吗?”
不,未必如此。团结和成员的义务既向外也向内。我可能对同胞负有某些特殊的义务,其中有些源自于我所居住的那些独特的共同体;但是我可能对另一些人负有别的义务—我的共同体对这些人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历史负担,就像在德国人和犹太人、美国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中那样。集体性的、对历史不公正的道歉和补偿,便很好地例证了这样一种方式:团结能够为共同体—而不是我自己,产生各种道德责任。改正我的国家的过往错误,是一种确定我忠诚于它的方式。
有时候,团结能够给予我们特殊的理由来批评我们自己人或我们政府的行为。爱国主义能够产生不同的意见。让我们以两种不同的引导人们反对和抗议越南战争的理由为例。一种理由认为,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而另一种则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我们去打,并且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相冲突。第一条理由可以为无论居住于何处的任何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所用,而这第二种理由,则只能被对该战争负责的国家的公民所感受并表达出来。一个瑞典人可能会反对越南战争并认为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但是只有美国人才会为它感到羞愧。
骄傲与羞愧这类道德情感预设了一种共享的身份。当那些在外国旅游的美国人见到美国旅客的粗鲁行为时,他们会感到尴尬,即使他们本人并不认识他们。非美国人可能认为这一行为是不体面的,但是他们却不会为它而感到尴尬。
那种对家庭成员和同胞的行为而感到骄傲和羞愧的能力,与集体责任的能力密切相关。这两种能力都要求我们将自己看做情境的自我—受制于那些我们并没有选择的道德纽带,并暗含于那些塑造我们作为道德主体的身份的各种叙述当中。
考虑到骄傲与羞愧的伦理与集体责任的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很困惑地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们(如亨利·海德、约翰·霍华德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人)居然基于个人主义的理由而反对集体道歉。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作为个体的我们,仅仅对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和行为负责,那么,我们就很难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传统而感到骄傲。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敬佩《独立宣言》、宪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以及那些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长眠的英雄们,等等。但是,爱国主义的骄傲,却需要一种穿越时间而延续的、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感。
与归属感相伴而来的是责任。如果你不愿意承担任何将自己国家的故事带入当今的责任,以及那种可能伴随着这一故事而来的各种道德负担,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而感到骄傲。
在大多数我们所考虑的情形中,忠诚的要求似乎补充了各种自然义务或人类权利,而不是与之相冲突。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情形凸显了自由主义哲学家们很乐意承认的一点:只要我们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那么我们就能通过帮助身边的那些人—如家庭成员或公民同胞—来履行那普遍的帮助他人的义务。一个家长救自己的孩子而不救他人的孩子并没有什么错,只要他在救孩子的路上不撞到陌生人的孩子。与此类似的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为自己的公民制定一种慷慨的国家福利也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尊重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权。只有当团结的义务导致我们侵犯一种自然义务时,它才是值得反驳的。
然而,如果那种叙述性的人的观念是对的,那么团结的义务,可能会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所提出的要求更为苛刻—甚至会与自然义务相冲突。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南部联军的指挥官罗伯特·李(Robert E.Lee)的事例。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李是北方联邦军队的士官。他反对南方脱离联邦—实际上,他认为这是一种谋反。当战争逼近的时候,林肯总统任命李来领导北方军队,而李拒绝了。他认为,他对弗吉尼亚州的义务要超过他对联邦的义务,同时他也声明自己反对奴隶制。他在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了他的决定:
尽管我对联邦无限忠诚,可是我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举起我的双手来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乡……如果联邦解散了,政府瓦解了,我会回到我的本州,分享我的人民的痛苦。只有在需要保护家乡的时候,我才会拔出我的利剑。 [336]
与法国抵抗运动的飞行员一样,李不能赞成那种可能要求他加害自己的亲戚、孩子和家乡的职责。但是他的忠诚要更进一步,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自己所反对的理由而领导他的人民。
由于南部邦联的目标不仅仅是脱离联邦,还包括保护奴隶制,所以我们很难为李的选择进行辩护。但是不敬佩那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的忠诚同样很难。可是,我们为什么应当尊敬那种对不公正目标的忠诚呢?你可能会很想知道,在这些情境中,忠诚是否应当具有道德分量。你可能会询问,为什么忠诚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一种遮蔽了我们的道德判断,并使我们难以做出正当之事的情感、感觉或强烈的感情呢?
原因是这样的:除非我们认真地将忠诚看做一种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要求,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将李的两难境界理解为一种道德上的两难。如果忠诚是一种没有真正的道德分量的情感,那么,李的困境就仅仅是道德和情感或偏见之间的冲突。不过,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那就误解了这里的道德利害关系。 [337]
如果我们对李的困境仅仅进行心理学的解读,那么就丢失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仅同情像李这样的人物,我们还敬佩他们;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的审慎所体现出来的性格品质。我们所敬佩的是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将自己的生活环境看做一种反思性的、情境的存在,并且能够接受这种环境—受那种将我置于一种特殊生活中的历史的制约,但却能意识到它的特殊性,并因此能注意到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更开阔的视野。要具有性格,就要接受自己的(有时候是相冲突的)各种束缚而生活。
最近一个对忠诚的道德分量的测试涉及两对兄弟间的故事:第一个是威廉和詹姆斯·“威蒂”·伯格的故事。比尔和威蒂在南波士顿安居工程中的一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中一起长大。比尔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学生,他学习经典并在波士顿学院获得了法学学位。而他的哥哥威蒂则中学辍学,整日流荡在街头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逐渐发展壮大。威廉·伯格进入政界,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主席(1978~1996),然后当了七年的马萨诸塞大学的校长。哥哥威蒂则因为抢劫银行而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成为冬山帮(Winter Hill Gang)的领袖人物—冬山帮是波士顿的犯罪团伙,它从事敲诈、操控毒品交易以及其他非法行为。威蒂被指控犯有19项谋杀罪,为了免遭逮捕他在1995年潜逃。他现在仍然逍遥法外,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 [338]
尽管威廉·伯格与他的哥哥通过电话,但是他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拒绝协助警方调查。2001年,当威廉在陪审团面前作证时,一名联邦检察官对他施压,要求他提供哥哥的消息:“让我们澄清一下,你对你哥哥的忠诚,要大于你对马萨诸塞州人民的忠诚吗?”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伯格回答道,“但是我确实对我的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关心他……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有所帮助……我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339]
在南波士顿的酒馆里,老主顾们对伯格的忠诚表达出一种敬佩之情。“我不怪他不告发他的哥哥,”一个居民告诉《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记者,“兄弟就是兄弟,你会揭发你的家人吗?” [340] 编委会和报纸记者们则更具批判性。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放弃了阳光大道,而选择了独木桥。” [341] 由于拒绝协助调查,伯格在公众的压力之下,于2003年辞去了马萨诸塞大学的校长一职,尽管他并没有由于阻碍调查而被起诉。 [342]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正之事就是帮助人们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家庭的忠诚能够凌驾于这一义务之上吗?威廉·伯格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很多年之前,另一个有着任性不羁的哥哥的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7年来,当局一直试图找到那个国内恐怖分子,他制造了导致3人死亡、23人受伤的一系列包裹炸弹案。由于他的目标包括科学家和其他学者,因此,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炸弹制造者以“炸弹客”著称。为了解释他行为背后的原因,该炸弹客在网上发表了一份3.5万字的反科技宣言,并做出承诺:如果《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发该宣言的话(它们确实这样做了) [343] ,他就停止爆炸。
46岁的社会工作者戴维·卡钦斯基(David Kaczynski)在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工作,当他读到这份宣言的时候,他发现它非常熟悉。它包含了一些听起来像他哥哥泰德的用语和观点;他的哥哥泰德54岁,是哈佛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后来成为一名隐士。泰德鄙视现代工业社会,居住在蒙大拿州一个山上的小木屋里。戴维已经有10年没有见到他了。 [344]
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挣扎之后,戴维于1996年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怀疑这名炸弹客是他的哥哥。联邦特工监视了泰德·卡钦斯基的小木屋并抓获了他。尽管戴维事前被告知,检察官不会判他哥哥死刑,可是他们还是判了。因为自己的告发,哥哥被判死刑,这让戴维备受煎熬。最后,检察官允许泰德·卡钦斯基服罪以换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345]
泰德·卡钦斯基在法庭上拒绝认自己的弟弟,并在他写于监狱的书稿中,将弟弟称为“另一个犹大”。 [346] 戴维·卡钦斯基试图重新构建他的生活,这一情节已经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努力取消哥哥的死刑之后,他成为一个反死刑组织的发言人。“兄弟之间理应互相保护,”他对一个听众描述了他的两难处境,“可是我的做法,却差点儿将哥哥送上了断头台。” [347] 他接受了司法部悬赏100万美元协助抓获炸弹客的奖励,但是他将大部分钱给了那些被他哥哥杀死或伤害的人。此外,他代表他的家族,为哥哥的罪行道了歉。 [348]
对于威廉·伯格和戴维·卡钦斯基对待自己哥哥的两种不同方式,你作何感想呢?对于伯格而言,对家庭的忠诚要超过将罪犯绳之以法的义务;而对于卡钦斯基来说,则刚好相反。可能那位逍遥法外的哥哥是否继续造成威胁,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差异。这似乎对戴维·卡钦斯基而言非常沉重:“我想,公平地说,我感觉是被迫的。又一个人可能会死去,而我本来能够阻止它—这种想法让我无法忍受。” [349]
无论你怎样评判他们所作的选择,你在解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很难不得出以下的结论:只有当你承认忠诚和团结的主张,能够与其他道德主张—包括将罪犯绳之以法的义务—具有同等的分量时,他们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被理解为道德困境。如果我们所有的义务都建立在同意或我们作为人对人所负有的普遍义务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明这类手足之情的困境。
迄今我们已经考量了一系列的事例,意图挑战契约论的这种观点:我们是那唯一约束我们的道德义务的创立者。这些事例有:公共道歉与补偿,为历史上不义行为所负的集体责任,家庭成员和公民同胞之间的特殊责任,对同志的忠诚,对自己村庄、社区和国家的拥护,爱国主义、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豪感和愧疚感,兄弟般和子女般的忠诚。在这些例子中所看到的团结的主张,是我们道德和政治经验中为人们所熟知的特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将难以生活,或难以理解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样难以用道德个人主义的语言去说明它们。它们不能被同意的伦理加以表达。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给予这些主张以道德力量的东西。它们吸收我们的各种负担,并反映出我们作为讲故事的存在,作为情境的自我的本性。
你可能想知道,这些跟公正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将我们引上这条道路的那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试图弄明白,我们所有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都能够追溯到一种意志或选择的行为。我已经论证过,它们不能;团结或成员的义务可能会出于与选择无关的理由—那些与我们借以阐释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居住的共同体的叙述密切相关的理由—而要求我们。
在关于道德主体的叙述性解释和那种强调意志和同意的解释之间,到底有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呢?其中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看待人类自由。当你在考虑那些声称要阐释团结和成员之义务的事例时,你可能会发觉自己在抵抗它们。如果你和我的许多学生一样,你可能会不喜欢或不相信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受制于各种未经自己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这种不喜欢可能会导致你反对爱国主义、团结、集体责任等主张,或者将这些主张重新改造为源自于某种形式的同意。拒绝或改造这些主张是具有诱惑力的,因为这样做会使它们变得与一种为人们所熟知的自由观相一致。也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不受任何未加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要获得自由,就是要成为那唯一能约束我们的义务的创立者。
我在试着通过本书中所考虑的这些或那些事例来提出,这种自由观是有缺陷的。但是,在这里,自由并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东西,同样岌岌可危的是:我们如何思考公正。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两种思考公正的方式。对于康德和罗尔斯而言,权利优先于善。那些界定我们的各种义务和权利的公正原则,应当中立于各种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康德认为,为了达到这一道德法则,我们必须抽离于自己各种偶然的利益和目的。罗尔斯坚持认为,为了慎议公正,我们应当搁置我们各种特殊的目的、情感以及各种善观念,这是在无知之幕背后思考公正的关键。
这种思考公正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思考公正的方式相冲突。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不能够或不应当中立于良善生活。与之相反,他坚持认为,公正宪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养成好公民、培育好品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慎议所分配的物品—如职务、荣誉、权利和机会—的意义,我们就不可能慎议公正。
康德和罗尔斯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考公正的方式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一种试图培养好品质或肯定某种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宪制,有着将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的危险。它也没有将人作为自由而独立的自我,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尊重。
如果康德和罗尔斯的这种构想自由的方式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关于公正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是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先在于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权利框架。如果自我优先于其目的,那么权利就必须优先于善。
然而,如果那种关于道德主体的叙述性的观念更有说服力,那么就值得我们重新考虑一下亚里士多德思考公正的方式。如果关于我的善的慎议,要反映出那些与我的身份绑定在一起的共同体的善,那么,那种中立性的期望就可能是错误的。不慎议良善生活而慎议公正,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值得欲求的。
将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带入关于公正和权利的公众对话中—这样的前景也许更让你震惊,而不是着迷,甚至令你感到害怕。毕竟,处于像我们这样的多元社会中的人们,在关于最佳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上存有分歧。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诞生,是一种试图避免政治和法律卷入各种道德和宗教纷争的尝试。康德和罗尔斯的哲学,是这一目标的最充分、最明确的表达。
不过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我们不可能不带有那些具有争议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去讨论许多最热门的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不同问题。在决定如何界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时,我们并不总是可能搁置各种不同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并且即使当这是可能的,也可能是不值得欲求的。
要求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在进入公共领域时,将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抛置脑后,这可能是一种保证宽容和相互尊重的途径。然而,实际上其反面却可能是真实的。一边裁定重要的公共问题,一边假装一种无法达成的中立性,是对强烈反抗和怨恨的一剂处方。缺乏实质性道德参与的政治,会产生一种贫瘠的公民生活。同时,它也容易引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会涌进自由主义者所不敢涉足的地方。
如果我们关于公正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使我们陷入各种实质性的道德问题,那么我们仍然要问,这些争论会如何推进。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公共领域推理善,而不陷入宗教战争之中?一个道德参与更多的公共对话是什么样的?它如何区分于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政治争论?这些不仅仅是哲学问题,它们是任何一种振兴政治对话、更新我们公民生活的尝试的核心部分。
1960年9月12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发表了一篇关于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演讲。“宗教问题”一直纠缠于他的竞选活动当中。肯尼迪是一名天主教徒,以前从来没有天主教徒当选过总统。有些选民心里怀有一种未说出口的偏见;而另一些选民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恐惧—肯尼迪可能会在公务处理上表达对梵蒂冈的感激,或者将天主教的教义强加于公共政策。 [350] 寄希望于消除这些恐惧,肯尼迪答应对一群新教牧师发表演讲,演讲内容为:如果他当选总统之后,他的宗教信仰将会在其总统任期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没有任何作用。他的宗教信仰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而与他的公共责任没有任何关系。
“我信任这样一位总统—他的宗教观是他自己的私人性事务。”肯尼迪说道,“当身为总统的我面对任何问题—例如节育、离婚、审查制度、赌博以及其他问题时,我都会根据我的良心所告诉我的那些国家利益而做出决定,而不涉及外在的宗教压力或命令。” [351]
肯尼迪并没有说,他的良心是否或怎样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塑造。不过他似乎是在暗示说,他关于国家利益的信念,与宗教没有多少关系—这里他将宗教与“外在的压力”和“命令”联系在了一起。他想要打消新教牧师和美国公众的顾虑,他不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无论它们是什么—强加给他们。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演讲是一次政治上的成功,肯尼迪继而赢得了总统职位。伟大的总统竞选记录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H. White),称赞这次演讲界定了“民主社会中一位现代天主教徒的个人教义”。 [352]
46年之后,巴拉克·奥巴马很快被所属的党派提名为总统候选人。2006年6月28日,就“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这一话题,他发表了一份截然不同的演讲。他一开始便回忆了两年前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活动中,自己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奥巴马的对手是一位非常尖锐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他攻击了奥巴马对同性恋权利和堕胎权利的支持,声称奥巴马不是一位好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也不会投他的票。
“我当时的回答,后来成为自由主义在这类争论中的一般性回应。”奥巴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说道,“我回答说,我们居住于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不能将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于人。我是在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而不是伊利诺伊州的牧师。” [353]
尽管奥巴马轻松地赢得了参议员的角逐,但现在他却认为他当时的回答是不充分的,并且“没有充分地说明,我的信仰在引导我自己的价值观和我自己的信念中所起的作用”。 [354]
他接着描述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为宗教与政治争论的关联而辩护。他认为,那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中“抛弃宗教对话的领域”的做法是个错误。“某些进步人士对任何一种宗教暗示的不安,经常阻止我们有效地用道德术语来表达问题。”如果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一种缺乏宗教内容的政治对话,那么,他们就丧失了那种数百万美国人赖以理解自己的个人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意象和专用术语。 [355]
宗教不只是一种引起共鸣的政治修辞。我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道德的转化。“我们害怕变得‘说教’……这导致我们低估各种价值观和文化在一些极其紧要的社会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奥巴马如是说。处理“贫困与种族、没有保险及失业”这类问题,需要“心灵上和思想上的改变”。 [356] 因此,那种坚持认为道德和宗教信念在政治和法律中不起作用的想法,是一种谬误。
世俗主义者要求有信仰的人在进入政治领域时,将自己的宗教置之度外;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改革家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多萝西·戴(Dorothy Day)、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不仅仅受到信念的激发,同时也反复运用宗教的语言来为自己的理由作辩护。因此,那种认为人们不应当将自己的“个人道德”注入公共政策争论之中的想法,是一种现实的荒诞。我们的法律在定义上就是一种道德的汇编,它的很多成分都是基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 [357]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约翰·肯尼迪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年轻有为、能言善辩、鼓舞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当选都标志着向一个新的领导时代的转型;并且,他们都努力召集美国人进入一个公民参与的新纪元。但是,他们在“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肯尼迪将宗教看做一个私人的而非公共的事务,这不仅反映出那种解除反天主教的偏见的需要,同时还反映出一种公共哲学,这种公共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亦即这样一种哲学:它认为政府应当中立于各种道德和宗教问题,以便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
两大主要政治党派都诉诸中立性的观念,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一般说来,共和党人在经济政策上援引这一观念,而民主党人则将它应用于社会和文化事务。 [358] 共和党人基于以下理由而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个体应当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经济选择,并如自己所愿地花自己的钱。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或为了公共的目的而控制经济行为,就是在强加一种由政府认可的、并不是人人都共享的、关于共同善的观点。减税对于政府花销来说是更为可取的,因为减税使个体能够自由地为自己决定去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以及如何花自己的钱。
民主党反对“自由市场中立于各种目的”这样一种观点,而支持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干预经济。然而,当论及社会和文化问题时,他们也援用那种中立性的言论。他们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在性行为或决定生育等领域“为道德立法”,因为这样做就是将某些人的道德和宗教观念强加于他人。政府不应当限制堕胎和同性恋的亲密行为,而应当在这些在道德上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当中保持中立,并让个体自由选择。
1971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肯尼迪的演讲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自由主义中立性的观念 [359] ,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20世纪80年代,批判自由主义中立性的共同体主义者,对作为罗尔斯的理论基础的那种自由选择的、不受约束的自我观念提出了质疑。他们不仅为更强的共同体和团结的观念作辩护,还为一种更强健有力的、对各种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公共参与而辩护。 [360]
1993年,罗尔斯出版了《政治自由主义》,它在某些方面改进了罗尔斯的理论。罗尔斯承认,在私人生活中,人们通常拥有“一些他们认为自己不会、确实不可以也不应当脱离的情感、奉献和忠诚……他们可能认为,将自己与某种宗教、哲学以及道德信念,或与某种持久的拥护与忠诚脱离开来,是不可思议的”。 [361] 在这种程度上,罗尔斯接受了那种构成深厚、道德上受约束的自我的可能性。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忠诚和拥护应当与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无关。在讨论公正和权利时,我们应当搁置自己的个人道德和宗教信念,而以一种“人的政治观念”为起点,独立于任何特殊的忠诚、情感或良善生活观念而展开讨论。 [362]
为什么我不应当带上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以使其对关于公正和权利的政治对话有所影响呢?为什么我们应当将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与那种被更广泛地认可的、作为道德的人的身份区分开来呢?罗尔斯认为,我们之所以应当这样做是为了尊重那关于良善生活的“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后者在现代社会普遍盛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人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存有分歧;再者,这些分歧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期望那些拥有全部理性能力的、有良心的人,在充分讨论之后,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363]
根据这一论争,支持自由主义中立性的理由源于那种在道德和宗教分歧面前,对宽容的需求。罗尔斯写道:“如果考虑周全的话,哪一种道德判断是正确的,就并不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为了在各种不同的道德和宗教学说中保持不偏不倚,政治自由主义就不“论及那些使这些学说产生分歧的道德话题”。 [364]
将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与我们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脱离开来的那种要求,意味着:当我们参与各种关于公正和权利的对话时,我们必须遵守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限制。不仅政府不可以接受一种特定的善观念,甚至公民们也不能将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仰,引入关于公正和权利的公共争论之中。 [365]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的论证盛行,那么他们在实际上就给自己的同胞们强加了一种基于某种特殊的道德和宗教学说的法律。
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政治争论是否满足了公共理性的要求,并恰当地被剥离了对任何道德或宗教观念的依赖呢?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检验方式:“为了检验自己是否遵循公共理性,我们可以询问:当我们的理由作为一种最高法院的观点而出现时,它将给我们怎样的印象?” [366] 正如罗尔斯所解释的,这是一种保证我们的论证,在自由主义公共理性所要求的那种意义上保持中立的方式:“法官们当然不能援引自己的私人道德,也不能援引一般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德性。他们必须将这些看做毫不相干的东西。同样的,他们也不能援引自己或他人的各种宗教或哲学观点。” [367] 当我们作为公民参与公共讨论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一种类似的约束。像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一样,我们应当搁置自己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并将自己局限于那些可以指望所有公民都接受的论点。
这是约翰·肯尼迪所援引的,而巴拉克·奥巴马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中立性的理想。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民主党人偏向了这种中立性的理想,并在很大程度上在他们的政治对话中排除了道德和宗教的争论。以下是一些著名的例外:马丁·路德·金在提出公民权利的理由时,援引了道德和宗教的论证;反越战运动由于道德和宗教对话而充满活力;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时,试图唤起这个国家追求那种要求更高的道德和公民理想。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者们接受了中立性和选择的言论,而将道德和宗教对话转让给了新兴的基督教右派 (13) 。
随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的政治中成为主导性的意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所说的“道德的大多数”、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的“基督教联盟”就是旨在填充那“赤裸裸的公共空间” [368] ,并与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生活中的道德放任而斗争。他们支持校园祈祷,在公共场所的宗教展示,以及对色情、堕胎和同性恋的法律限制。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是通过逐个挑战道德判断而反对这些政策,与此相反,他们是通过主张道德和宗教判断在政治领域中毫无地位,而反对这些政策。
这种论证模式很好地满足了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们,并给自由主义带来一个坏名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自由主义者们出于自卫地论证道:他们也拥护各种“价值”,他们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宽容、公平以及选择的自由。(在一次令人尴尬的、引起共鸣的发言中,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其政党大会上的提名演讲中,使用“价值”或“价值观”这类词语的次数高达32次。)但是,这些价值都与自由主义中立性以及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约束相联系。它们与那种广泛的、道德的和宗教上的渴望无关,也没有回应那种对于一个具有更高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期望。 [369]
与其他民主党人不同,巴拉克·奥巴马理解这种渴望,并给予其以政治的表达。这就将他的政治,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他能言善辩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他善于用词,还在于他的政治语言注入了一种道德和宗教的维度,而这种道德和宗教的维度的旨向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中立性。
每一天,似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为日常事务而奔波—送孩子上学、开车上班、飞去参加一个工作会议、逛街购物、努力减肥—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缺失了某些东西。他们判断出自己的工作、财产、消遣、十足的忙碌,其实并不够。他们想要一种目的感,一种关于自己生活的叙述性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想与那些处于自己地位的人对话—以一种与他们自己的各种希望和价值观相关联的方式,去交流我们的各种希望和价值观—那么,作为先进者的我们,就不能抛弃宗教对话的领域。 [370]
奥巴马主张,先进者们应当接受一种更加宽泛的、对信仰友好的公共理性。这反映出一种正确的政治本能;它同样也是一种好的政治哲学。那种试图将关于公正与权利的论证与关于良善生活的论证脱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原因有两种:第一,我们并不总是可能不解决实质性的道德问题,而裁决公正与权利的问题;第二,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值得欲求的。
让我们来考虑两个人们所熟悉的,如果不在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争论中表明立场就无法得到解决的政治问题—堕胎与胚胎干细胞研究。有些人认为,我们应当禁止堕胎,因为它涉及夺去一个无辜的人类生命;而其他人则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法律不应当在“人类生命源于何时”这一道德和宗教争论中表明立场。他们认为,由于发育中胎儿的道德状态,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因此政府应当中立于这一问题,并允许妇女们自主决定是否堕胎。
第二种立场反映出那种为人所熟知的,关于堕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论点。它主张,在解决堕胎问题时,要基于中立性和自由选择,而不介入该道德和宗教争论。不过这种论点赞同者寥寥。因为,如果发育中的胎儿在道德上等同于一个孩子,那么堕胎在道德上就等同于杀婴。因而很少有人会坚持认为,政府应当让父母们自己决定是否去杀死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堕胎争论中主张妇女有权选择是否堕胎的立场,就并不真正地中立于那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它暗自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天主教关于胎儿的道德状态的教义—它从怀孕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人—是错误的。
接受这种假设并不是为禁止堕胎而论证,这只是承认,中立性和选择的自由并不是肯定堕胎权利的充分基础。那些维护妇女自主地选择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的人,应当介入这样的争论—发育中的胎儿等同于一个人,并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一观点是不对的。认为法律应当中立于道德和宗教问题并不够,允许堕胎的理由与禁止堕胎的理由同样不能中立。两种立场都预设了某种对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争论的回答。
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也是如此。那些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认为,无论其医学前景是什么,那些涉及毁灭人类胚胎的研究,在道德上都是不容许的。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人格开始于怀孕;因此,即使是毁灭一个早期的胚胎,在道德上也等同于杀死一个孩子。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支持者们通过指出这一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医学益处,包括可能治疗或治愈糖尿病、帕金森症以及脊髓损伤等,而做出回应。他们认为,科学不应当受到宗教或意识形态干预的制约;人们不应当允许那些持有宗教性反对意见的人,将他们自己的观点通过那可能禁止有前景的科学研究的法律,而强加于人。
然而,正如关于堕胎的争论一样,人也不可能不在“何时可以算做一个人”的这一道德和宗教争论中表明立场,而得出允许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理由。如果早期的胚胎在道德上等同于一个人,那么那些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可能就是有道理的;即使是有很好前景的医学研究,也不能为肢解一个人而辩护。很少有人会说,从一个五岁的孩子身上获取器官以促进挽救生命的研究,应当是合法的。因此,那种允许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理由,在“何时可以算做一个人”这一道德与宗教争论中也不是中立的。它预设了一种对这个争论的回应—在胚胎干细胞过程中被毁坏的、着床前的细胞,还并不是一个人。 [371]
我们不可能不在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上表明立场而解决堕胎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中,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讨论的行为是否涉及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当然,大多数道德和宗教的争论并不涉及生死问题,因此,自由主义中立性的铁杆拥护者们可能会回应说:堕胎和干细胞研究是特殊情况;除非是那些危及人类定义的情况,否则我们就能不在道德和宗教争论中表明立场而解决各种关于公正与权利的争论。
但是,这也是不对的。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你能够不涉及那些关于婚姻的目的以及同性恋的道德状态的争论,而判断出国家是否应当认可同性婚姻吗?有些人说可以,并基于自由主义的、不加评判的理由而为同性婚姻辩护:无论一个人本人是支持还是反对男女同性恋的关系,个体都应当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允许异性结婚而不允许同性结婚,就是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并否认了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如果这一理由是政府认可同性婚姻的一个充足的基础,那么这一问题就能够在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范畴内得到解决,而无须求助于各种有争议性的,关于婚姻的目的及其所尊敬的善的观念。但是,我们也不能基于不加评判的理由,而做出那种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这取决于一种特定的观念:婚姻的目的—婚姻的意图或意义。并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提醒我们的,要讨论一项社会制度的目的,就要讨论它所尊敬和奖励的各种德性。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争论—男女同性恋的结合,是否值得拥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由政府认可的那些婚姻所具有的荣誉和认可。因此,那种基础性的道德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要弄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就要记住:一个国家在婚姻问题上可以有三项可能的政策,而并非只有两项。它可以沿用传统的政策,而只认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姻;或者它可以像许多国家已经做的那样,以认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婚姻的同样方式,来认可同性婚姻;或者它可以拒绝认可任何形式的婚姻,而将这一职责留给私人性的组织。
我们可以将这三项政策总结如下:
1. 只认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姻。
2. 认可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
3. 不认可任何形式的婚姻,而将这一职责留给私人性的组织。
除了婚姻法,国家还可以对那些居住在一起的未婚夫妇,采用那些准予法律保护、继承权、医院探视权和孩子监护安排的公民联姻法或同居法,并进入一种法律的安排。很多州已经给男女同性恋提供了这种安排。2003年,马萨诸塞州经过州最高法院裁定,成为第一个赋予同性婚姻以合法性认可的州。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法院也裁定:支持同性婚姻的权利。但数月之后,大多数选民在一次自发的全州范围内的投票表决中,推翻了该项决定。2009年,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而非司法裁决,而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 [372]
第三项政策完全是假想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至今没有哪一个州宣布放弃将认可婚姻当做一项政府职能。但是这项政策却值得我们研究,因为它能为支持或反对同性婚姻的论证提供线索。
第三项政策是对婚姻争论的理想的自由至上主义解决方式。它并不废除婚姻,但是它确实废除了将婚姻作为一项政府认可的制度。我们最好称之为婚姻与政治制度的分离。 [373] 政教分离就意味着除去一座官方的教堂(而同时允许教堂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与此类似,使婚姻与政治制度分离,就意味着不再将认可婚姻作为一种官方职能。
这一观点的创立者是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抱怨说,将婚姻限制为异性婚姻就是一种歧视;而反对者则主张,如果政府认可同性婚姻,那么这就超越了对同性恋的宽容而接受了它,并给它贴上了“一枚政府同意的标签”。金斯利写道,对此的解决方式就是“终止政府认可婚姻的制度”,“将婚姻私人化”。 [374] 让人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结婚,而不带有政府的认可或干涉。
让教堂和其他宗教机构继续提供婚姻仪式。如果百货公司和赌场愿意的话,让它们也介入这种行为……让夫妇们以任何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结合,并允许他们在任何自己想要的时刻认为自己结婚了……是的,如果三个人想结婚、或一个人想与自己结婚,并且有其他人想要举行一个仪式并宣布他们结婚了,那么,就让他们去做吧。 [375]
“如果婚姻完全是一件私人性的事务,”金斯利推理道,“那么,所有的关于同性恋婚姻的争论都将成为毫不相干的。同性婚姻不会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异性婚姻也不会得到。”金斯利提议,同居法可以解决那些在人们同居和共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保险、抚养孩子以及继承等问题。他实际上提议,要用公民联姻来取代所有的政府认可的、同性的或异性的婚姻。 [376]
从自由主义中立性的角度而言,金斯利的提议具有一种明显的、超越于其他两种标准的备选项(政策一和政策二)的优势:它不要求法官或公民参与关于婚姻目的以及同性恋道德的各种道德的和宗教的争论中来。由于政府不再将婚姻的荣誉性的名称授予任何家庭联合体,因而公民们就得以避免介入关于婚姻目的以及男女同性恋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争论当中。
相对而言,同性婚姻的争论双方都很少有人接受这种将婚姻与政治制度分离的提议。但是它却说明了现存争论当中的、那种受到威胁的东西;它也帮助我们弄明白,为什么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必须苦于应付那些基础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争论,后者与婚姻目的以及定义婚姻的各种善有关。这两种标准的立场,都不能在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范畴内得到辩护。
当然,那些基于这样的理由—同性婚姻认可罪恶、不尊重婚姻的真正意义—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正在提出一种道德或宗教的主张而感到羞愧。可是,那些维护同性婚姻权利的人,却经常试图将自己的理由建立在中立的基础之上,并避免对婚姻的道德意义做出评判。那种企图为同性婚姻找到一种不加评判的理由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不歧视和自由选择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本身并不能为同性婚姻的权利而辩护。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就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在审理“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部”这桩同性婚姻案时,所写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略有不同的观点。 [377]
马歇尔以认识到这一主题所引发的深层次的道德和宗教分歧为开始,并暗示该法庭不会在这场争论中表明立场:
许多人都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和伦理信念,认为婚姻应当局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同性恋行为是不道德的。许多人持有同样强烈的宗教、道德和伦理信念,认为同性情侣有资格结婚,同性恋者应当得到与异性恋者毫无差别的对待。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回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界定全体人们的自由,而不是强制执行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 [378]
似乎是为了避免卷入关于同性恋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争论,马歇尔用自由主义的术语,在法庭面前描述了这一道德问题—她把它当做一种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的问题。她写道,将同性情侣排除在婚姻之外,与“尊重个体的意志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一致。 [379] 如果政府可以“阻止个体自由地选择一个人,与之分享一种排外性的承诺”,那种“选择是否结婚以及与谁结婚”的自由就将是空洞的。 [380] 马歇尔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涉及选择的道德价值,而是个体做出选择的权利—也即,原告们“与他们所选择的伴侣结婚”的权利。 [381]
但是,意志自由与自由选择并不足以为同性婚姻的权利作辩护。如果政府真的在所有自愿的亲密关系的道德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那么,政府就没有理由将婚姻限制在两个人之间;经过同意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同样也是合格的。事实上,如果政府真的想保持中立,并尊重个体所愿意做出的任何选择,那么,它就不得不接受迈克尔·金斯利的提议,脱离于认可任何婚姻的这一事务。
在同性婚姻的争论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的自由,而在于同性结合是否值得共同体的尊敬和认可—他们是否实现了婚姻这项社会制度的目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一问题在于职务和荣誉的正当分配,它是一种社会认可。
尽管马萨诸塞州的法庭强调选择的自由,可是它并没有打算去敞开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婚姻方式;它并没有质疑这样一种观念:政府可以给予某些亲密联合,而不是其他亲密联合以社会认可。该法庭也没有号召废除婚姻,或将婚姻与政治制度分离。
与之相反,大法官马歇尔的观点却将婚姻称赞为“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最有益的、最珍贵的制度之一”。 [382] 它认为,消除政府认可的婚姻“将会取消我们社会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383]
马歇尔并不呼吁废除政府认可的婚姻,与之相反,她呼吁扩展婚姻的传统定义,以囊括那些同性伴侣。在这样做的时候,她已经站立于自由主义中立性的范畴之外,而肯定同性联合的道德价值,并提出了一种被恰当地构想的、与婚姻目的相关的观点。她注意到,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互相愿意的成人之间的一种私人性安排,而是一种公共认可和同意的形式。“在其真正意义上,在每一个公民的婚姻当中都有三个参与者:两个愿意的配偶,外加一个同意的政府。” [384] 婚姻的特征带来了它的荣誉性的一面:“公民的婚姻,是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深层次的个人承诺;同时也是一种对相互关系、友情、性行为、忠诚和家庭这类理想高度的公共庆祝。” [385]
如果婚姻是一项表示敬意的制度,那么它尊敬什么样的德性呢?询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询问,婚姻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意图或目的。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主张,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繁衍后代。根据这种论点,由于同性婚姻不能繁衍自己的后代,所以他们没有结婚的权利。可以说,他们缺乏相应的德性。
这种目的论的论证路线,是反对同性婚姻的核心理由,玛格丽特也直截了当地采用了它。她并没有假装在婚姻的目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提供了一种相反的阐释。她坚持认为,婚姻的本质并不是繁衍后代,而是两个伴侣之间—无论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一种排外性的、充满爱意的承诺。
现在,你可能会问,我们怎么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关于婚姻的目的或本质的说明中做出裁决呢?我们有可能理性地讨论那些在道德上具有争议的社会制度—如婚姻—的意义和目的吗?或者,这是否仅仅是各种赤裸裸的断言之间的碰撞呢—有些人说它与生育有关,而另一些人则说它与充满爱意的承诺有关—而且没有途径能够说明一种比另一种更加合理?
马歇尔的观点很好地阐释了这类论证是如何展开的。首先,她反驳了这样一种主张—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她通过说明,正如当前由政府所实施和管理的,婚姻并不要求生育能力,而反驳了以上观点。那些申请结婚证的异性恋夫妇,并没有被询问“他们通过性交而孕育孩子的能力或意图。生育能力并不是婚姻的条件,也不是离婚的原因。那些从来没有圆房,也不打算圆房的人们,可能是结婚并维持婚姻的。那些行将就木之人也可以结婚”。“或许大多数已婚夫妇都有共同的孩子(通过辅助手段的或不通过非辅助手段),”马歇尔总结道,“可是,公民婚姻的必要条件是婚姻伴侣相互间那种排外性的、永久的承诺,而非生养孩子。” [386]
因此,马歇尔的部分理由,是对现存婚姻目的和本质的一种阐释。当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关于一项社会行为的阐释—作为生育的婚姻与作为排外性的、永久承诺的婚姻—时,我们如何能决定哪一种更为合理呢?一种途径就是询问,哪一种说明在总体上更好地理解了现存的婚姻法。另一种途径就是询问,哪一种对婚姻的阐释,颂扬了各种值得尊敬的德性。什么才算做婚姻的目的,这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认为婚姻应当赞颂和肯定什么样的品质。这就使得我们无法避免那种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的争论:男女同性恋关系的道德状态是什么?
马歇尔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保持中立。她认为,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将婚姻限制在异性恋者之间,就“在那种破坏性的固有看法上贴上了一枚官方同意的标签,这种固有看法认为:同性婚姻在本性上是不稳定的,比异性关系低级,因而不值得尊重”。 [387]
因此,当我们仔细研究同性婚姻的案例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能基于那些非歧视的、自由选择的观念之上。为了决定谁有资格结婚,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婚姻的目的及其所尊敬的各种德性。而这就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道德境地,在这里,我们不能在那些不同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之中保持中立。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三种公正进路:第一种认为公正意味着使功利或福利最大化—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第二种认为公正意味着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或者是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实际选择(如自由至上主义者们的观点),或者是人们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所可能做出的假想的选择(如平等主义者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公正涉及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同善。正如你们所料,我支持第三种理论进路。现在让我来试着说明原因。
功利主义的进路有两个缺陷:第一,它使公正和权利成为一种算计,而非原则;第二,由于将所有的人类善都纳入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价值衡量标准,它对所有的人类善等量齐观,并没有考虑它们之间质的区别。
那种基于自由的理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遗留下了第二个。他们认真看待权利,并坚持认为公正不仅仅是一种算计。尽管他们内部在“哪些权利应当超越功利主义的考量”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某些权利是根本性的,而必须得到尊重。然而,在将一些权利划分为值得尊重的之后,他们接受人们现有的各种偏好。他们并不要求我们质问或怀疑我们带进公共生活里的那些偏好和欲望。根据这些理论,我们所追求的那些目的的道德价值、我们所过的生活的含义和意义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共同生活的质量与品质,都存在于公正领域之外。
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使功利最大化,或保障选择的自由,就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为了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我们不得不共同推理良善生活的意义,不得不创造一种公共文化以容纳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各种分歧。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原则或程序,这种原则或程序能够一劳永逸地证明任何产生于它的有关收入、权利以及机会的分配原则,那将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一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的话—将能够使我们避免那些由关于良善生活的讨论而必定会引起的混乱与争论。
然而,这些争论是无法避免的。公正不可避免地具有判断性。无论我们所争论的是政府救助、紫心勋章、代孕母亲、同性婚姻、反歧视政策、军事服务、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还是使用高尔夫代步车的权利等等,公正问题都跟不同的关于荣誉和德性、自豪和认可的观念绑定在一起。公正不仅包括正当地分配事物,它还涉及正确地评价事物。
如果一个公正的社会涉及对良善生活的共同推理,那么,我们仍然需要询问:什么样的政治话语能够如此指引我们?对这一问题,我并没有一个完备的答案,不过我能提出一些例证性的说明。首先是一种观察:如今,我们的大多数政治争论,都是围绕着福利与自由—例如增加经济收益和尊重人权。对很多人来说,在政治领域谈论德性,会让他们联想到宗教保守主义者们在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然而,这并非德性观念和共同善能够表征政治的唯一途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构想出一种政治,它认真对待道德和精神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应用于广泛的经济与公民关怀,而不仅仅是性和堕胎等问题。
在我的一生之中,我所听到的在这方面最有希望的言论,来自于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所发表的言论。对他而言,公正不仅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和分配,它还包括更高的道德目的。1968年3月18日,肯尼迪在堪萨斯大学发表演讲,他提到了越南战争、美国城市暴乱、民族不平等以及他在密西西比和阿帕拉契等地区所看到的极度贫困。接着他从这些具体的公正问题转移开来,声称美国人已经开始珍惜错误的东西。肯尼迪说道:“即使我们努力消除物质匮乏,我们也还面临另一种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面对满意度的匮乏……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异常苦恼。”美国人让自己“仅仅限于算计物品”。 [388]
目前我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 000亿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包括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它包括我们用来锁门窗和那些关押撬锁罪犯的监狱的专用锁,它包括对红木的毁坏和在动乱中损失的那些自然奇迹,它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警用装甲车以镇压城市暴乱,它还包括……那些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389]
当你聆听肯尼迪的此次演讲,或阅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他对当时的自满情绪以及物质迷恋所进行的道德批判,与他认为贫困、越南战争以及民族歧视是不公正的观点相脱离。然而,他认为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肯尼迪认为,要扭转这些不公正之事,我们有必要质疑身边所看到的那种自满的生活方式。他毫不犹豫地加以评判,并且,他在激发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的同时,也诉诸一种共同体感。
在此次演讲之后不到三个月,肯尼迪遇刺。我们现在只能猜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所暗示的那种道德共鸣的政治是否已经实现。
40年之后,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巴拉克·奥巴马同样触及了美国人对那种具有更高目的的公共生活的渴望,并阐明了一种具有道德和精神希冀的政治。然而,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应付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需要,是否会妨碍他将那在竞选中所表达出来的道德和公民主旨转变成一种共同善的政治?
一种新型的共同善的政治会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一些可能性的主题:
如果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一种较强的共同体感,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培育公民关心全局以及为共同善作奉献。它不能对公民们带进公共生活里的那些态度、倾向以及各种“心灵习惯”漠不关心,而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反对那些将良善生活观念完全私人化的做法,并培育公民德性。
传统中,公立学校一直是公民教育的据点。对某几代人来说,军队是另外一个。我这里主要讨论的不是关于公民美德的具体教导,而是那些实际的、通常又是无意的公民教育;当那些来自于不同经济阶层、宗教背景和民族共同体的年轻人来到共同的制度之中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公民教育。
当公立学校处于劣势,而且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服兵役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像我们这样一个辽阔而又迥然不同的民主社会,此时如何能够期望培养出一个公正社会所需要的团结以及相互之间的责任感?这个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体现于我们当今的政治话语之中。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巴拉克·奥巴马注意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以及一种新的为国效力的意愿。他批评乔治·W·布什没有号召美国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共同牺牲。他说道:“他号召我们去购物,而非服务于国家;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战争时期对美国富人减税,而没有被号召着去共同牺牲。” [390]
奥巴马提议学生们用100个小时的公共服务来换取大学学费资助,并以此鼓励他们为国效力。当他在国内巡回演讲的时候,他这样告诫年轻人:“你投资给美国,美国也投资给你。”事实证明,他这个建议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2009年4月,他签署了一项法律以扩展“美国志愿队”这一公共服务项目,并给那些在社区当志愿者的学生提供大学费用。然而,尽管奥巴马为国效力的号召引起了共鸣,但更为激进的、强制为国服务的提议仍然没有被提上政治议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趋势,就是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例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探讨过,当国家雇人来服兵役,以及把对囚犯的审讯承包给商人或私人承包商的时候,或者当父母将怀孕和生育孩子承包给发展中国家那些获得报酬的妇女的时候,或者人们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肾器官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些道德问题。还有很多别的事例:我们应当给那些就读于不太好的学校,却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报酬吗?我们应当给那些提高了学生们考试成绩的老师发放奖金吗?各州应当雇用那些营利性的监狱工厂来安置它们的囚犯吗?国家应当接受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提议,将每个公民身份标价为10万美元而加以出售,并以此来简化其移民政策吗? [391]
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功利和同意,它们还涉及评价那些重要的社会行为—如服兵役、生育孩子、教导与学习、惩罚罪犯、批准新公民等—的正确方式。由于市场化的社会行为,可能会腐蚀或破坏那些界定它们的规范,因此我们需要拷问,我们想要保护哪些非市场的规范不受市场的侵蚀呢?这个问题,需要公众讨论各种不同的、评价各种善的正确方式。市场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有用工具,然而,除非我们想让市场改写那些支配社会制度的规范,否则我们就需要公开讨论市场的道德限制。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已经达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高水平。然而,不平等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凸显出来。即使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温和地提议要使个人所得税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时,共和党的反对者们也称他为企图扩展财富的社会主义者。
当代政治领域中对于不平等问题少有关注,然而这并不说明政治哲学家们对此问题也缺乏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何正当分配收入和财富”这一问题,就一直是政治哲学领域的争论热点。然而,哲学家们倾向于将这一问题置于功利或同意的框架之内,这使得他们忽视了以下这一点: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很有可能获得一种政治上的关注,并最接近于道德和公民复兴这一谋划的核心。
有些哲学家从功利的角度主张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他们推测,如果从一个富人那里拿走100美元赠给一个穷人,这只会极其轻微地减少这个富人的快乐,而极大地增加那个穷人的快乐。约翰·罗尔斯也赞成再分配,但是他是基于一种假想的同意。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设想一个假想的社会契约,那么,每个人都会同意一种支持某种形式的再分配的原则。
然而,我们还有第三种更为重要的理由,来为美国生活中日渐增长的不平等而感到担忧:贫富之间的过大差距会破坏民主性的公民身份所需要的团结。其原因如下:随着不平等的逐步加深,富人和穷人的生活会进一步分离。富人们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者是在富裕郊区的公立学校),而将城市里的公立学校留给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家庭的孩子。类似的趋势导致了那些由于其他公共制度和设施的特权而产生的分离。 [392] 私人健身俱乐部代替了市政娱乐中心和游泳馆;高档住宅区雇用私人保安,因而较少地依赖于公共警察的保护;人们所拥有的第二辆或第三辆车,消除了人们对公共交通工具的依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富人脱离于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而将这些留给那些消费不起其他事物的人们。
这一点有两个不良后果,一个是财政上的,而另一个是公民方面的。第一,由于那些不再使用这些公共服务的人们不太愿意纳税以维持它们,因此这些公共服务会衰落。第二,诸如学校、公园、操场以及社区中心这样的公共机构,不再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公民们相互邂逅的场所。那些曾经聚集公众、并充当公民美德教育的非正式学校这一角色的场所,变得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公共领域的虚空,使得我们很难培养团结和共同体感,而这些正是民主公民社会所依赖的基础。
因此,除了对功利和同意的影响之外,不平等还能够腐蚀公民美德。那些迷恋市场的保守主义者们,以及关心再分配的自由主义者们,都忽视了这一损失。
如果公共领域的侵蚀是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种共同善的政治,会将公民社会基础设施的重建,作为其首要目标之一。它将向富人征税来重建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以使得富人和穷人都想要利用它们,而不是为了扩充私人消费的机会而关注再分配。
我们的上一辈人在政府公路项目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给美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个人流动性和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对私家车的依赖、市郊的扩张、环境的破坏以及腐蚀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投资于那种在结果上平等并有利于公民复兴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富人和穷人都想把孩子送进去的公立学校,可靠到足以吸引高收入上班一族的公共交通系统,公共健康医疗所、操场、公园、娱乐中心、图书馆和博物馆等能够(至少是理想地)将人们吸引至封闭的社区之外,而进入一种共享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公共场所。
如果我们集中关注不平等的公民性后果及其逆转方式,那么,那些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论,就不会找到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也有助于凸显分配公正与共同善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公众参与讨论有关良善生活的问题,就是一种公民违法,是一次超越自由主义公共理性之界线的历程。我们通常认为,政治和法律不应当陷入各种道德和宗教争论,因为这样会导致压迫和不宽容。这是一种合理的担忧。多元社会中的公民对于道德和宗教问题确实存在分歧。正如我所论证的,即使政府不可能中立于这些分歧,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基于相互尊重而引导政治呢?
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它比我们现在所适应的这个社会更有活力、参与性更强。近几十年来,我们开始认为,尊重我们同胞们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就意味着忽视它们(至少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打扰它们,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公共生活中不涉及它们。然而,这种回避的立场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尊重。它经常意味着压制,而非避免道德分歧。而这能够引发人们激烈的反对和怨恨,它也能够导致一种贫瘠的公共话语,后者从一个新闻周期转至下一个周期,并充斥着各种丑闻、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及日常琐事。
一种对于道德分歧的更加有力的公共参与,能够为相互尊重提供一种更强而非更弱的基础。我们应当更加直接地关注同胞们所带入公共社会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有时质疑并反对之,有时聆听并学习之,而不是加以避免。我们并不能保证,关于棘手道德问题的公共慎议,在任何情形中都会达成共识—或欣赏他人的道德和宗教观点。我们对一种道德和宗教信念的深入了解,却总是有可能使得我们更不喜欢它。然而,我们只有等尝试之后才能知道答案。
与回避的政治相比较,道德参与的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理想,它也为一个公正社会提供了一种更有希望的基础。
这本书其实源于一门课程。近30年来,我一直有幸给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们教授政治哲学,其中很多年我都在教一门名为“公正”的课程。该课程让学生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公正的哲学著作,并参与讨论了一些当代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争论,这些争论引发了各种哲学问题。
政治哲学是一门论辩性的科目,“公正”这一课程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学生们开始反驳—反驳那些哲学家们,反驳其他同学,甚至反驳我的观点。因此,我首先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参加“公正”这一课程的几千名本科生。我希望,这本书的精神体现出了他们对公正问题的积极参与。我也感激那些帮助我教授这门课的几百名研究生以及法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每周例会上所提出的那些深刻尖锐的问题,不仅使我时刻保持警觉,同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们带给学生们的那些哲学主题。
无论主题是否一样,写一本书与教一门课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一开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让我绞尽脑汁。我感谢哈佛法学院的暑期研修班,它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感谢纽约卡内基公司的“卡内基学者项目”,它支持了我关于“市场的道德局限”的研究;我尤其感谢瓦坦·格雷戈里安(Vartan Gregorian)、帕特里夏·罗森菲尔德(Patricia Rosenfield)、希瑟·麦凯(Heather McKay)对我的友善、耐心和帮助。这本书中关于市场和道德的那部分内容,是一个项目的开始,而到现在我还没有完成这个项目。
我受益于法勒–斯特劳斯–吉鲁(Farrar,Straus and Giroux)的一个杰出的工作小组。自始至终,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保罗·伊利(Paul Elie)、杰夫·索约(Jeff Seroy)、劳雷尔·库克(Laurel Cook)以及我的文稿代理人埃丝特·纽伯格(Esther Newberg),都是一些让我觉得合作很愉快的人。他们对书的热爱、对做书的热爱,鼓舞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并给作者提供便利。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帮助。
我的两个儿子亚当(Adam)和阿伦(Aaron),从他们能拿起汤匙的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争论了。他们对道德的认真劲儿、聪明劲儿以及热情劲儿,一直都具有挑战性,并使问题更加丰富,同时也让我觉得关注他们的讨论是一种乐趣。当我们感到疑惑的时候,我们都转向基库(Kiku)—我们道德和精神上的试金石,我的灵魂伴侣。我将此书献给她,带着我无尽的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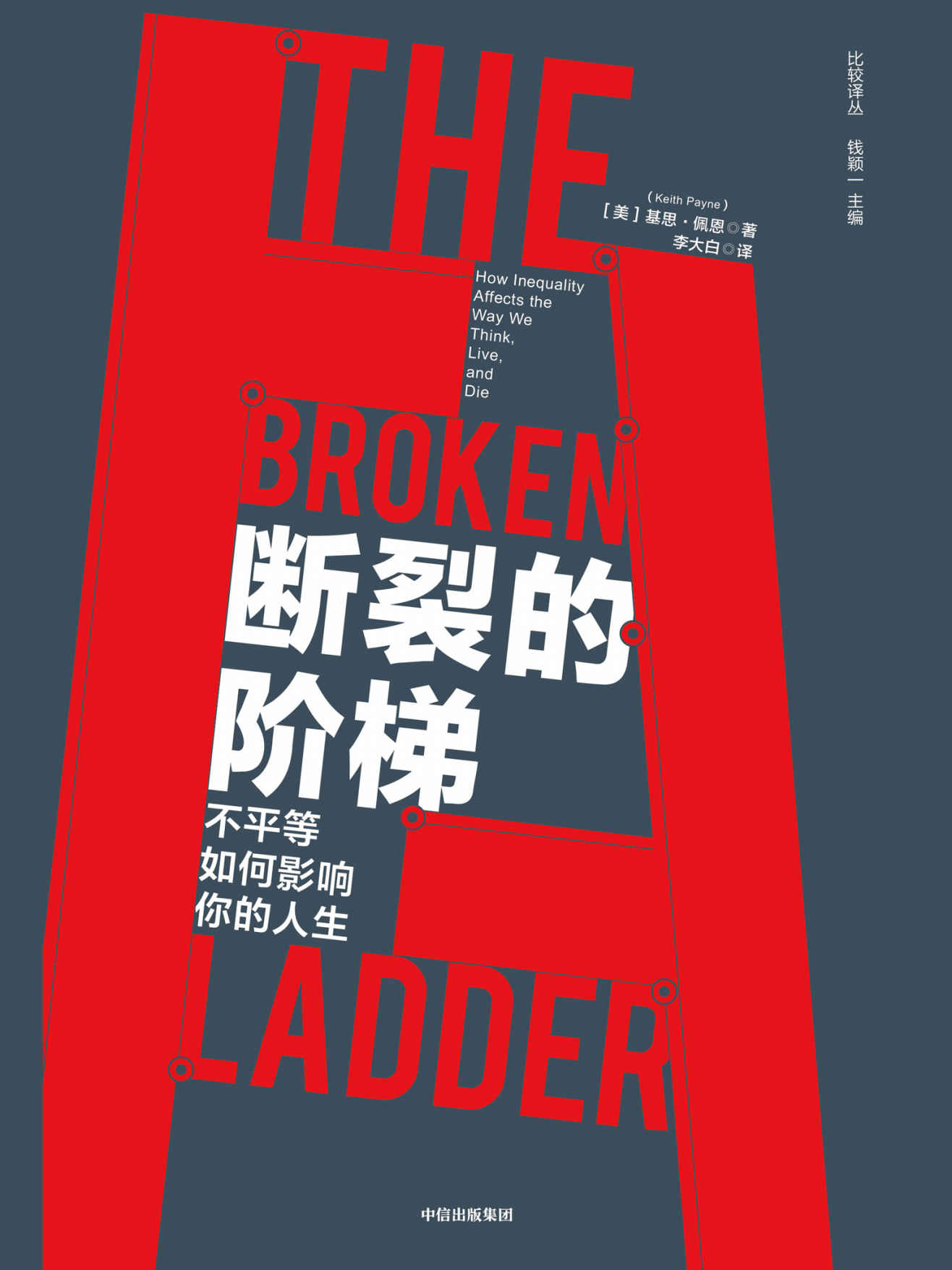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 [1] 。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一段两个小时的飞行,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华盛顿飞往杰克逊维尔的航班上,没人知道约瑟夫·沙基 [1] 为什么忽然转身,一把夹住了身后那名乘客的头,也许是因为那名乘客说话声太大,也可能是他突然用脚抬高了沙基的座椅靠背。然而,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这名乘客并没有挑起任何事端。
这时,机组人员迅速出现,以制止这场骚动。但沙基并没有被吓住,他用膝盖抵住一名空乘的下身,胁迫他走到紧急出口处,试图在飞行期间打开舱门。最后,空乘和几位乘客制服了沙基,给他戴上了塑料手铐。飞机一落地,沙基就被捕了,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
发生在头等舱的不良行为总是与众不同。2009年,在一架即将从棕榈滩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坐在头等舱的伊凡娜·特朗普 [2] ,为屏蔽邻座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噪音,戴上了头戴式耳机。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孩子让她忍无可忍,她忽然情绪失控、大发雷霆,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把她送下飞机,这时,她还在朝着孩子们嚷嚷:“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飞机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每天遭遇的焦虑也在这里集中体现。我们被扔到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被迫把我们爱的人、普通同事等人压缩到同一级别的亲密关系之中。我们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狭窄的金属管道,在密闭空间中发酵的恐惧不断滋长,随时面临被引爆的危险。
一旦飞机升入空中,你便无处可逃,而时间也似乎无穷无尽。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几千英尺的高空时,对高度的恐惧便被触发了。机身踉跄着,颠簸着,摇摆着,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这段被未知事物扭结的感觉。从出发到落地,我们一直身处这样一段“失控”的时空中,直到被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后,这种“失控”感才逐渐消失。在飞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等待着,并不确定与我们同行的人是谁,这趟航班的飞行情况如何?谁应占用哪个扶手?无论如何,我们时刻被自己的道德感提醒着,何种生命体验更具存在主义色彩?
在飞行引起的焦虑之外,飞机还从另一方面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小宇宙”——飞机是身份等级的物理体现。他们是由铝合金和纺织品构成的社会阶梯——你所在的排数、机组和舱位代表了你所在的阶层。
画一幅机舱内部的座位示意图,更便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机舱内攻击陌生人、诅咒小孩子。最近,一个由心理学家凯瑟琳·迪塞尔(Katherine DelCells)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主导的研究 [3] 显示:飞行中的身份等级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飞行时的行为。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空中发飙”的概率,研究者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飞行数据。首先,他们比较了有无头等舱的机型并据此推理:如果地位不平等会导致坏行为,那么我们应该会在有头等舱的飞机上看到更多的“空中发飙”事件才对。他们发现,有头等舱的飞机上发生“空中发飙”事件的概率,比没有头等舱的飞机要高出四倍。飞机晚点等其他相关因素当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头等舱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发生骚乱的可能性,它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9个半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验证这个推理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观察登机过程,来发现地位差异是如何被强化的。大部分有头等舱的飞机,都是头等舱乘客先登机,这就迫使经济舱的乘客必须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过这些已经舒适落座的富人面前的过道,才能跋涉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由于15%的飞机是从机身中部或尾部登机,就使得这些飞机上的普通乘客可免于这种“折磨”。如预测所示,在“前登机式”机舱内,“空中发飙”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其他登机方式的两倍,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6个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空中发飙”的研究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揭示了不平等如何像楔子一样插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让我感兴趣的是,“空中发飙”事件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时也会发生——一张普通的经济舱机票也得花上几百美元,“真正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负担一次新式商用客机的旅程。然而,即便是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其相关差异也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责难和争吵。而且,争吵也不只是局限在经济舱。在研究中,当“前登机式”飞机的头等舱旅客与正在登机的“乌合之众”亲密接触时,他们也多次濒临“爆发”。上述伊凡娜·特朗普的行为证实,当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大到无法忽略时,每个人的行为都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
但这种行为的“不正常”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不平等正以一种系统性的、可预见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它让我们变得短视,喜欢冒险,情愿为了当下的满足,而牺牲确定的未来。它让我们更倾向于做出一些“自我攻击”的决定,它让我们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迷信般地执着于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而拒绝接受真实的世界。不平等将我们生生划分为因收入、意识形态和种族不同而不同的阵营,瓦解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这种分层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觉得既不健康,也不快乐。
假定有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住的都是上述各个“阵营”的人群——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被种族和意识形态隔离的、所谓“不值得信任”的人,没空听你讲理的迷信群众,以及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时倾向于自我毁灭的人——这个社区画像中的形象,反映了贫困者的基本倾向,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城市中的典型贫困社区或沮丧的乡村活动住屋。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不平等在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中也会导致同样的倾向。
关于“空中发飙”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平等不等于贫穷,即便两者看上去有很大的重合之处。本书的主题正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即便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赤贫阶级,但“不平等”也会让人们“感到贫穷”或“表现得贫穷”。在我们的观念中,不平等与贫穷是如此相像,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其大部分特质也更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
正如多数报道所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今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掌握的财富,比这个星球上最贫困的35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 [4]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超过20%的财富被1%的人掌握。
要综合分析如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范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就像试图测量一光年的距离,或者抓住大脑中的千亿神经元,或者测量这些神经元之间几百万亿的连接。这类数据显然非人力所及。因此,让我们首先在更加合理的框架下审视经济,同时探寻在这一框架之下,人们是如何看待其经济地位的。
很多人类特征,譬如身高,可以粗略地描绘为一条“钟形曲线”(正态曲线)。这条曲线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部分——因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平均值区域,而两端的长尾呈坡状逐渐下降。这个模型也在很大范围内适用于其他描述。譬如指纹上波峰的数量 [5] ,爱尔兰啤酒的化学成分 [6] ,或是苏格兰士兵的胸围 [7] ,等等。“钟形曲线”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界的通用法则,而如今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这个模型是如此通用,以至于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何早先的思想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人们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时,似乎就是在一个“钟形曲线”的参数中进行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起一项调查 [8] ,要求美国人识别其所在的阶层。一个经典的“钟形图”便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是,约有89%的回应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只有2%的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层阶级”的位置上。可以说,在美国人的眼中,大家几乎全都是“中产阶级”。
让我们来看一下图1的实际收入分布 [9] ,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描述。把它置于全人类的范围,我已经为这个图表划定了范围,最顶端的0.1%达到的高度是一个6英尺 [01] 高的男人的头顶位置。纵轴表示的是年收入;横轴表示处于每一收入水平的家庭数量。从横轴左边开始数一英寸 [02] 的位置,对应的约是美国最贫穷的20%人口;到模特脚尖处,就达到了“中位收入”,美国的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上,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下。底部80%的家庭的年收入都在10万美元以下:如果你的家庭收入能达到6位数,那么你就是收入在前20%的人群,你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码尺的4英寸高处了。
图形左侧的翼形意味着绝大部分人口挤在底部。向上延伸的细线说明收入达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数量极少。这就没有什么“钟形曲线”了,80%的家庭居于模特脚踝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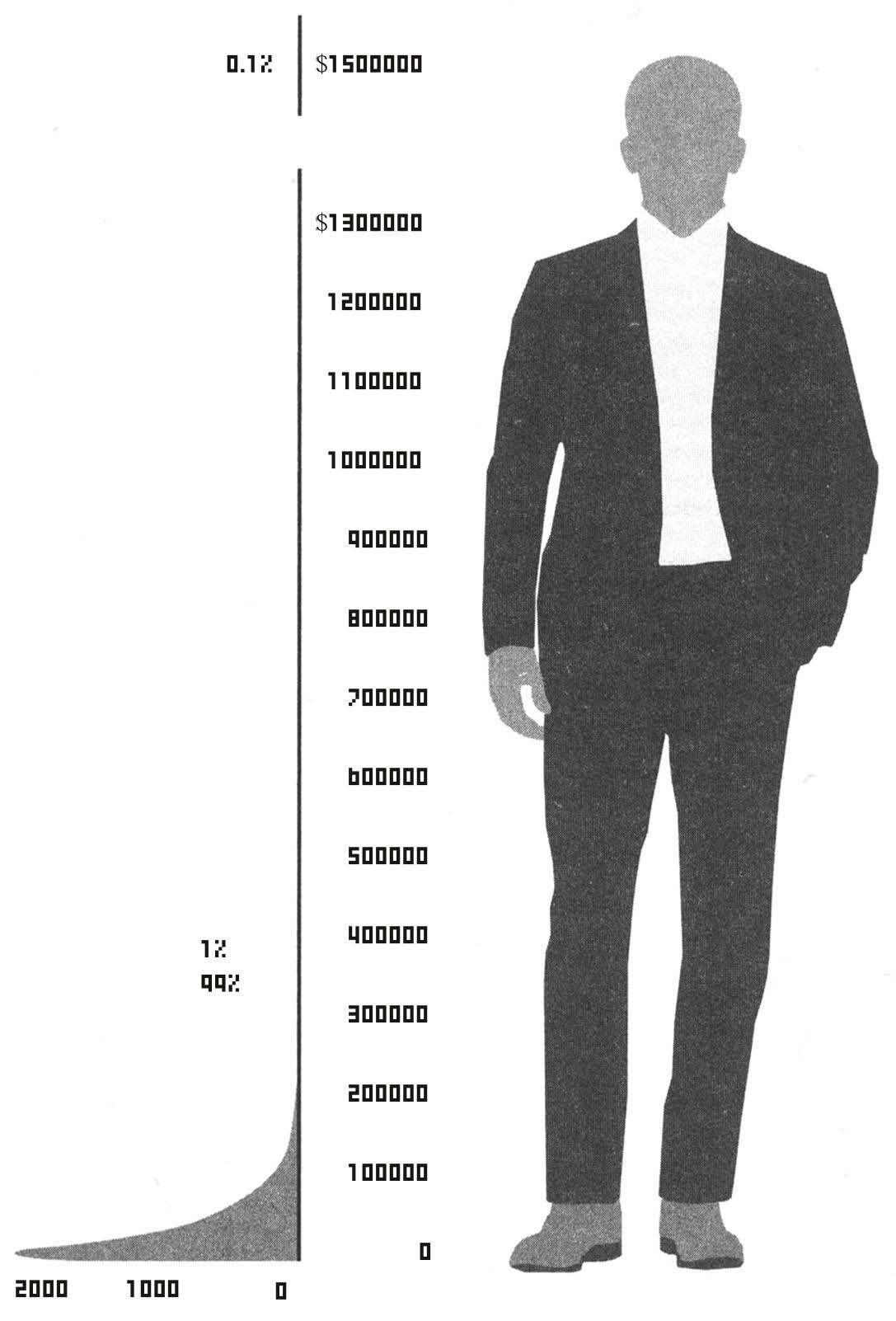
图1 用人类身高来表示的美国收入分布图
尽管图形顶端的上限是150万美元,其实有部分人挣得比这更多。如果把那些“超级富豪”计算在内,你手上这本书必须设计得更长、更高,以保持图表缩放在页面的范围之内,否则底部的99%就小到让人注意不到了。因此,就像大部分对于收入分配的表述一样,图1的表述遗漏了大部分像阿莱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这样的专业运动员,也并没有把“名人榜”上排第一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算进去,还忽略了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如果这个图包含了当今最高薪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年收入,那么它就不只是达到这个六英尺高的男人的头顶,而是应该达到一座塔楼的塔顶了。
收入分配总是一边倒,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底部有一个天然的、更低的边界,因为你总不可能搞得比0还少——至少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第二,“钱”是能“生钱”的。因为财富是可以被投资的,也只有投资才能使财富成倍地增加。金钱创造了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富人更富,还产生了长尾效应,那些无甚可投资的人则不能加入这个圈子之中,只能一直聚集在收入曲线的底部。
即便收入分配永远是倾斜的,在如今的美国,分配不公平程度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而且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更加严重。图2说明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在每10年中的变化,包括最富有的5%的人群(具体美元数根据通胀率有所调整)。 [10] 在图2中,你会看到图1中的长尾再度出现:富人变得更富,同时穷人变得更……好吧,就当穷人们正在做些有趣的事情。而美国人中最穷的那5%,已经在过去50年里变得更加稳居底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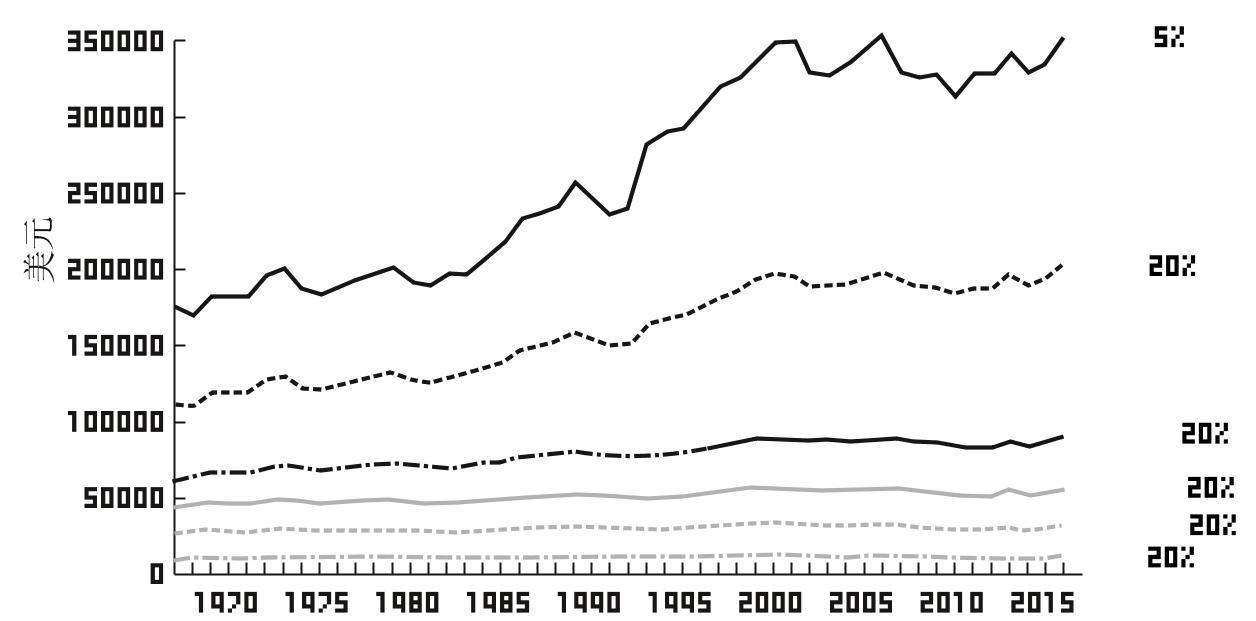
图2 1967—2015年家庭平均收入(2015年美元)
资料来源:U.S.Census。
你也许并不期望看到穷人落得这样的结果(也不期望看到中产阶级这样的结果,他们基本上原地不动),就像那句众所周知的格言清晰地表达的那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是大部分人在新闻头条上获得的信息——美国的不平等正在扩大。我们耳边整天充斥着那些所谓“日益加剧的经济焦虑”、“日益加剧的绝望”和“对未来逐渐失去希望”。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30岁以下的美国人有一半认为:“美国梦”已经破灭。 [11] 这种焦虑是真实的,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地去了解它。但是即便依据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最穷的5%的人也仍然停留在1967年,那一年,他们被远远地甩在了大多数人身后。
虽然穷人可能不会在事实上变得更穷,关于不平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即便你待在原地不动,如果你周围的人一直在进步,你也会感到自己落后了。你是否经历过这种情况——你坐在一列静止的火车上,这时你旁边的火车开动了,你就会感觉自己在往后移动。当上层阶级稳步变富,中产阶级和赤贫阶级就会通过比较而感觉自己愈加穷困。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幻影。就像我们即将在本书前几章看到的那样,这个“幻影”将产生致命的后果。
论述经济不平等原因的书籍能放满满几架子,基本集中在大范围的历史趋势之中,譬如科技和全球贸易模式的进步,或者是税收和超前消费等政策上。本书并不涉及这些分析,相反,它将检视不平等对我们(作为人类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旨在研究“别人家的财富”——前5%、1%或者0.1%的那部分人的财富——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为什么富人的财富会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呢?毕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当然,我们身边运动着的火车与我们自己对运动的感觉之间也没有逻辑关系,但它确实产生了影响。这显然不能用火车的属性解释。相反,这些解释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找到,它有能力把你的知觉“嘿!我们在动!”变为行动“抓住扶手!”。
这是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在你“贫困”的日子里,是不是自己“感觉贫困”的时间比你“真正贫困”的时间还长?为什么你邻居房子的大小会影响你的应激激素?为什么财产不安全会让我们做出将自己推到更加不安全境地的决定?为什么你在财务上的成功会让你把那些不认同你的人当成傻瓜,而你却很难做到把他们当成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
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这本书也不能提供新的政策建议,以改变税率或者改善社会保障。然而,它将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譬如有助于解释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现代高科技世界中的一些悖论——平板电视对你来说很便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获得财务安全。在这个平均住房面积达2600平方英尺的世界上,很多家庭仍负担不起一次要花400美元现金的急诊。 [12]
虽然评估不平等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因和经济后果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我的目标更加个人化。这个目标就是把我们所知的收入分配与调查数据,同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个体的真实情况连接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朋友和同事,一同走向未知的未来,理解财富分配如何形塑我们的思想,可以让我们更加游刃有余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些理念,它们就能够逐步减少不平等本身。现在,我们将从已经认识到的“飞机冲突”、“不动的车厢”以及“他人豪华的住宅”这些人类经验出发。所有这些经验都让我们感到,自己似乎正处于坠落之中。
[1] “Virginia Man Arrested at Jacksonville Airport for Assault on Flight Crew,”Department of Justice,U.S.Attorney's Office,Middle District of Florida,February 1,2016,www.justice.gov/usao-mdfl/pr/virginia-man-arrested-jacksonville-airport-assault-flight-crew.
[2] D.Garner,“Socialite Ivana Trump Kicked Off an Airliner After Foul-Mouthed Tirade at Noisy Children,”Daily Mail,December 28,2009,www.dailymail.co.uk/tvshowbiz/article-1238731/Ivana-Trump-flies-rage-cabin-crew-unruly-children-board-plane-say-police.html.
[3] K.A.DeCelles and M.I.Norton,“Physical and Situational Inequality on Airplanes Predicts Air Rage,”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13(2006):5588-91.
[4] “Working for the Few,”Oxfam International,January 20,2014,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summ.en.pdf.
[5] Francis Galton,Fingerprint Directories(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1895).
[6] S.T.Ziliak,“Guinnessometrics: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Student's 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008):199-216.The“bell curve”is usually used to refer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but the brewer William Gosset discovered its close cousin the t-distribution by sampling Guinness.Both are generally bell shaped.
[7] S.Stahl,“The 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Mathematics Magazine 79(2006):96-113.
[8] R.Morin and S.Motel,“A Third of Americans Now Say They Are in the Lower Classes,”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10,2012,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9/10/a-third-of-americans-now-say-they-are-in-the-lower-classes/.Eighty-nine percent said they were either“lower-middle,middle,or upper-middle”class.
[9] For other ways to make abstract economic ideas more concrete,see http://visualizingeconomics.com/.
[01]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合0.3048米。——编者注
[02]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合2.54厘米。——编者注
[10] Data from C.DeNavas-Walt and B.D.Proctor,“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13,”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U.S.Census Bureau,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
[11] “Survey of Young Americans’Attitudes Toward Politics and Public Service,28th Edition,”October 30-November 9,2015,Harva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http://iop.harvard.edu/sites/default/files_new/pictures/151208_Harvard_IOP_Fall_2015_Topline.pdf.
[12]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Households in 2014,”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May 2015,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2014-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1505.pdf.
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其实属于穷人,是在食堂新阿姨上任的那天,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在此之前,学校里的收银台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我知道有一些孩子领餐的时候付钱,但也有像我一样的孩子是不用付钱的。但是无论是否需要付钱,以前的食堂阿姨都会让我们顺利通过,毫无障碍,就像把塑料饭盒滑过光滑的铁轨那样爽快。后来,这位食堂阿姨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好对付的年轻女人。当我拿着饭盒走过她身边时,她叫住了我,要收1.25美元的饭费。我感觉自己有点失衡了,就像站在一个极速前进又忽然停止的电梯上,由于惯性作用,马上要跌倒。我有点结巴了,但结巴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有。在那个时刻,只要能赶紧逃离这个地方,给她多少钱我都愿意。这时,一个年长一些穿着粉色polo衫的高个女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带着发套的弗拉明戈舞者,靠过来在这个年轻女人耳畔低语一阵,我才被放行。最后,午餐队伍又归于平静。但是对我来说,在这个新收银员逐渐熟悉谁该付多少钱之前的一周,真是度日如年。
我意识到我的免费午餐意味着什么的那一刻,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会面红耳赤。现在我的家庭情况虽然比那时好太多了,但那个时刻的确改变了我的一切。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之间的不同。除了统一穿校服的时间,那些为自己午餐付费的同学看上去穿得更光鲜。也许是因为他们穿着好鞋吧?他们还留着更好的发型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去美发沙龙理发,而不是在家里用剪刀和碗比着头剪呢?我们的成长环境彼此只不过间隔着几公里,但是我们这些吃免费午餐的孩子都继承了父母拖沓的南方口音。而吃付费午餐的孩子则有着一般意义上的“播音腔”,你可以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好像是没有故乡似的。
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孩子,在学校几乎永远保持沉默。我能跟谁说话呢?忽然之间,一个新的社会阶梯横亘在我面前,压迫着我。这个阶梯的横梁被鞋子、发型和口音打上了标签,就像用电报打出的密码一样,而我却一直试图在解码。然而,做这件事除了改变我的看法之外,对我的处境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即便到现在,我还是穷困的。
如果你还是像会计师那样,只是单纯从财务角度考虑富有和贫穷,那么我的回答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的观察并不能改变我父母的收入,也不能改变我每个月的花销。除了改变我自己之外,我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能改变世界上的任何事。但是,通过改变我的关注点和看法,我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变化,而这最终改变了我的未来。
为了弄懂我们是如何考量地位的,让我们来看看下一页的梯子图。设想一下,站在梯子顶端的人比别人强。他们拥有最多的金钱、最好的教育以及最高薪的工作。在梯子底端的人则是生活境遇最差的。他们的金钱最少,接受最低级的教育,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如果他们还有个工作的话。现在让你来参考其他人的情况,评估一下自己的经济地位,你会把自己放在这架梯子十级阶梯的哪一级呢?
这个简单的图是在主观社会地位评估中使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我们称之为“地位阶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声望,我们应该能够比较准确地预估出,他会把自己放在哪级阶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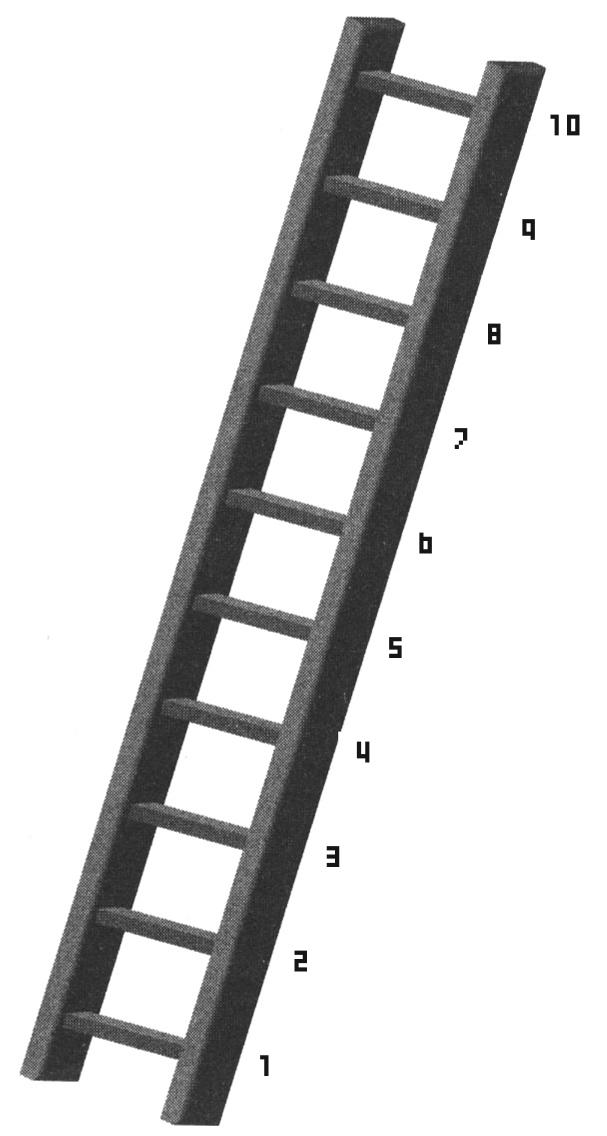
图1.1 对于地位阶梯的图像描述,一般用来衡量关于相对地位的主观认知
除非我们没有机会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平均说来,有更高收入、接受过更多教育、从事更有尊严的工作的人,确实把自己放在这架梯子比较高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效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譬如有一千个人,一些人会把自己放在顶端,另一些人则会把自己放在底端,而大部分人还是会把他们放在中间的位置。但是,大概只有20%的人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教育和工作地位进行自我评估的。
令人惊讶的是,在传统的地位划定与地位如何被主观感知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这意味着有很多依据客观标准看比较富裕的人,也会把自己置于比较低的阶梯上。 [1] 类似地,许多在客观上很贫穷的人,也会把自己放在梯子的高处。
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也许会认为,人们对自我的概念,实际上是空虚无物的,仅仅像在两段广播之间轻微的、嘶嘶啦啦的噪音那样若有若无。如果主观感知不能与像金钱这种客观可衡量的数量相匹配,那么这些感知就会变得更差。可以肯定的是,金钱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情节。
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对地位的主观感知,因为它们揭示了很多关于人类命运的故事。如果你把自己置于比较低的阶梯上, [2] 你就更可能在未来几年遭遇沮丧、焦虑和长期的痛苦。你选择的阶梯越低,你就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在工作中发挥失常;你就越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的事物和阴谋论,你面临体重问题、糖尿病和心脏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你选择的阶梯越低,你剩下的人生就越少了。
让我澄清一下,我并不是在简单地断言。如果你是贫穷的,那么上述事情就更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我正在论述的是,即便你是“感觉贫穷”而非事实上的贫穷,这些事情也更容易发生在你身上。当然,人们“感觉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贫穷。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仅仅是故事的20%。对于其余,我们则必须看一看普通中产阶级人士的情况,并追问事情的原因。抛开真正的金钱本身不谈,他们中的大部分觉得自己只是在混日子而已,生活只不过是在支付上一张账单和下一张账单之间度过,如果邻居们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如果他们但凡多挣一点点钱,一切似乎都能变得美好一点。为了搞懂这个地位阶梯,我们必须站在超越银行账户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人。
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挣多少钱,但是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挣够了”。这是因为我们判断到底“够不够”的唯一标准是通过跟他人比较。我们是如此习惯地与他人攀比,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少注意到我们正在“攀比”。当我们看到一个邻居开着一辆新车,我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说:“他们都有一辆奥迪车了,我也得来一辆。”我们当然比这种想法更加世故和成熟些。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我们邻居的好运气跟我们没关系。”或者说:“她工作那么努力,理应拥有这样的新车。”如果我们确实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去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可能也会趁着这种想法刚出现的时候就赶紧打消。然而,当下一次我们上自己的车时,可能就比昨天没看见邻居新车的时候更加觉得:“我这车的座椅怎么这么破旧!”社会比较就是这么难以避免。
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很难察觉到这种存在于工作之中的比较,因为它们发生在幕后,而我们却在台前体验着。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餐馆内部的噪声越来越大时,我们就会感到一起吃饭的伙伴说话的声音聊胜于无,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在伙伴的面部,而非周围环境。
尽管我们对富有或贫穷的感觉基于我们所做的比较,但事实是,社会比较总是发生在幕后,从而产生了真实存在的“盲区”。让我们来想想,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价值观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什么是驱动你前进的动力?关于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我询问了成百上千的人,通常的回答包括譬如爱、信念、忠诚、诚实和自尊等观念。尽管个人的答案有些出入,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足以容纳所有答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家都是类似的。然而,不管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还是仅仅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都没人曾经提到过那些我们都知道的实情——“我渴望得到社会地位”。
其他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能在他们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譬如从他们购买的衣服、居住的房子和送出的礼物中,我们就能观察到这一点。总之,我们能从持续变换着的、到底什么才能算作“足够”的标准中感知到这一点。如果你得到过一次升迁,几个月之内你就会适应这个新的薪水层级,然后再次感到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样,生活在不停付账单的日子当中。当你达到更高的成就时,你比较的标准同样也会升高。与组成银行账单的固定数列不同,地位总是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因为它是以与他人的实时比较来定义的。
我们总是在任何场合下,与所有各类人进行着社会比较,但我们总是神奇地在地位阶梯的上半段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我们觉得把自己安放在此地是最舒适的。试想一下,你到底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你到底有多聪明?道德感有多强?你对朋友有多忠诚?你是一个好司机吗?接着数下去,你会发现自己在以上所有方面都比一般人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深深地知道,他们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是比一般人强。但这种感知范围扩大到所有人身上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这个发现被称为“沃比根湖效应” [3] 。在盖瑞森·谢勒虚构的这座小镇上,“所有女人都是强壮的,所有男人都是英俊的,所有孩子都是超群的”。这个效应在1965年的一次关于事故幸存者的研究中被偶然发现。 [4] 研究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采访西雅图医院里正在治疗车祸伤病的患者。他们把这些患者与一组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和同受教育程度的对照组进行比较。其中的一个采访问题,就是要求患者评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即便这并不是这个研究原本的主要意图,但该问题正是这一研究被人铭记至今的原因。因为这些住在医院里的车祸伤病患者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超过大多数驾驶员。事实上,他们的程度只不过跟那些对照组的成员,即没遭遇过驾驶事故的人差不多罢了。很显然,这些患者并没有仅仅因为在一次车祸中进了医院这件事,就影响他们对自己是一个好司机的自我认知。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事故的确不是出于这些患者的过错呢?调查者研究了每宗案件的警察局笔录,以确定到底是谁应该对事故负责,谁是不应被责备的受害者。在分别确认这些驾驶者中谁是肇事者之后,很显然,这些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受伤者是肇事者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人都高。
关于“沃比根湖效应”的另外一个早期例子,是由主办美国大学生入学考试(SAT)的美国大学委员会在一次大规模调查中发现的。 [5] 差不多有100万在指定年份参加SAT的学生被要求把自己与“中位数学生”(在这一点上下,“更好”和“更差”的学生数量各半)相比较。这个定位不仅包括在SAT的分数表现,也包括诸如领导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等个人特质。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力处于中位数之前那半段,有85%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比另一半人强。
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与同事们要求一组志愿者从几个维度评估自己是“多好的一个人”。 [6] 志愿者们认为自己更具道德感、更和善、更独立也更值得信赖,而且也比普通人更加诚信,这是一个并不令人惊奇的结果,尽管这些志愿者曾经进过监狱,并被判过重罪。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在大多数事情上优于其他人,只是在“遵守法律”方面稍逊一筹,但还是跟普通人差不多。试想一下,当他们做出这些判断的时候,他们正被关在监狱里,其客观性自然要大打折扣。
此去经年,成百上千的研究已经重复证实了“沃比根湖效应”。这些研究显示,大部分人相信我们在智力、忍耐力、责任心和羽毛球技术等诸如此类的积极品质上要高于平均水平。我们越是看重某项特质,我们就会越夸大自己在这种特质上的能力。在这类研究中,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在我所在大学的教授之间进行的,这一研究要求大家与其他同事相比,评估自己的教学能力,竟然有94%的人认为他们的教学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 [7] 这种倾向转变成为所有偏见之母: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是更加客观的,而且比普通人更不具偏见。 [8]
自然,在脑海中把自己放在梯子的上部,并不是我们进行大部分社会比较的唯一途径。有时我们也会看低其他人。我最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听闻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正在变胖,多丽·帕顿(Dolly Parton)变得消瘦,而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正在挥霍她的才华。一些家庭主妇看上去也正在就此争论着。为什么这些名人的“新闻”就像碎纸屑一样撒得我们满身都是,但是我们从未看到当地暖通维修工戴尔与家庭保健护士布兰达之间的分分合合呢?
答案自然是我们总被身居高位的人们吸引。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地位上升的人就被戏剧奉为英雄,因为只有高起点的人才有可能“斯文扫地”。与艺术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把自己的眼睛盯在富人、名人的身上,而直接忽略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为什么我们对地位如此在意呢?这一点在大部分关于此类争论的书籍中被称为“人类之所以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的原因”。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对地位的渴望则不能把人类归于其外了。事实上,它是我们本性中如此古老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与其他具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共有这种特性。看看狒狒或黑猩猩的公开决斗,那种残暴地为它们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而进行的体力争斗,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当我们看到它们交配的时候会感到不适:人类看到它们的不雅行为时会感到尴尬,但又能确切地认识到,究竟是什么在驱使着它们的行为。
在对名人的关注方面,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表现惊人相似。在一项由脑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普拉特(Michael Platt)领衔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恒河猴看不同种类的图片, [9] 同时,追踪它们眼睛的运动。第一组照片只包括它们所在领地的高等级猴子;第二组照片只有它们的低等级同伴。这些猴子每看一张图片,就可以吸一次果汁(对于一只口渴的恒河猴来说,冰果汁是一项丰厚的回报,比猴子们哪天的食物都强)。研究者系统地调整猴子喝到的果汁量:看低等级的照片会比看高等级的照片得到更多的果汁。
猴子们的表现也很明晰。它们想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即便这种做法会让它们牺牲很多果汁。实际上,与看空无一物的屏幕相比,猴子们必须得到更多的果汁,才能忍耐着去看低等级猴子的照片。只有一件事能让雄性猴子比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更有兴趣,那就是雌性猴子的生殖器。
猴子们的这些行为与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人类与恒河猴共享93%的基因。 [10] 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与猴子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把对这些恒河猴的观察跟与其类似的专注于地位的那些与人类更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诸如黑猩猩、狒狒等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一个持续不断的模式。恒河猴与人类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2500万年前,比在600万至800万年前才与人类分开的黑猩猩祖先要早多了。人类和恒河猴对地位有类似的迷恋,这意味着该特质很有可能早已在我们共同的祖先身上有所表现,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特质。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从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打猎和采集植物的小团体中。 [11] 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至少10万年,而且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是高度平等的。我们从化石遗迹和在它们周围找到的手工艺品中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每个人身边的陪葬品都差不多。当后来社会变得更加阶级化时,国王和法老的墓葬里就会发现数量繁多的珠宝,有时还会看到他们最喜欢的狗、妻子或奴隶,而这时低等阶级的墓穴中基本就没什么陪葬品,如果幸运的话,有的人会裹一条毯子。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些“平等的采猎者”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把他们想象成一些可爱的、平和的、乐于分享的人,就像缠着遮羞布的嬉皮士那样,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的物欲所污染。实际上,采猎者之间之所以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比我们今天更慈善,而是因为采猎者很难比团体中的其他人积累更多的财富。设想一下,这个采猎者的团体在今天猎杀的战果和能保存到明天的浆果之外没有实在的财富,共享劳动果实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果我杀了一头乳齿象,应该怎么处理它的肉呢?存储这些肉的最好方式便是让它进入我家人朋友的胃中。这样就把我的善心转化成流通货币了,等到下次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同样地对待我。
这种互惠共存的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人们记得谁得到了什么东西,以及每个人投入其中的努力,当有人比其他人得到的东西更多时,他们就会变得沮丧。一个关于卷尾猴(那种你曾经见过的,在街头咿咿呀呀地表演老式风琴的猴子)的研究提示,这种社会核算的才能也是古老的。像人类一样,猴子在没能达到其真正目的的时候也会“抓狂”。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布鲁斯南(Sarah Brosnan)为卷尾猴设计了一种简单的交换游戏。 [12] 首先,她会给猴子一颗小石子,然后伸出手来,当猴子把小石子还回来的时候,她就会给它递一片黄瓜。当他们进行这种交换游戏的时候,猴子总是会坚持用石子换黄瓜。
在这项实验的关键环节中,布鲁斯南让两只猴子参与同一场游戏,让它们能看到彼此的交易过程。首先,布鲁斯南与其中一只猴子交换石子和黄瓜。然后她就与第二只猴子玩一遍同样的游戏,但是把回报换成了葡萄(换葡萄是因为考虑到对猴子来说,葡萄比黄瓜更可口)。布鲁斯南再回到第一只猴子身边,试图与它再次开始原初的游戏,以证实它是否会做出“理性”(从狭义的经济意义来讲)选择继续拿黄瓜,毕竟有的吃总比没的吃要好,或者它会采取更具社会智性的行动并抗议,放弃营养补充,以求行使一种平等的模式?
然而这一次,这只被“欺骗”了的猴子没有拿黄瓜:它看了一眼黄瓜片,然后直接把它扔给了布鲁斯南。这个小单元在许多对猴子中实验了许多次。有时,被试的猴子直接就把黄瓜给扔了,有时会把黄瓜扔到实验者的脸上。有时猴子甚至连石子也不归还。猴子的心声:“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低收益的交换埋单?”
当猴子们发现其他猴子得到葡萄时,在几分钟前还被它们欣然接受的黄瓜明显就不够看了。这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猴子们更关心它们在与其他猴子的比较中处于何种位置,而不是它们实际可得到的回报。它们对公平的感知敏锐度远远超过我们此前的多番猜测。
灵长类动物学家关心的不是如何从人类角度来描述他们所研究动物的内在状态。因此,当一只猴子上蹿下跳,龇牙咧嘴,充满攻击性地扑过来时,灵长类动物学家会把这种行为叫作“侵略性展示”,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这只猴子是愤怒的。如果你观看了布鲁斯南的实验录像,那么,你就很难把猴子们的行为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情绪表达。猴子们把黄瓜扔回给实验者,然后抓住笼子的栏杆拼命摇晃,就像一个被囚禁者要掀起一场暴动那样大喊大叫。我不是灵长类动物专家,所以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群猴子疯了!”
关于卷尾猴反对收到不平等报酬的发现与人类十分相似,说明这些倾向是进化而非习得的。如果人类是生而在意平等的,那么,即便在很小的孩子身上,我们也应该能发现此类证据。而且,事实上,3岁儿童就已经表现出与卷尾猴十分相像的行为了。举个例子,有一项研究要求几对孩子帮助一位实验者清扫几个街区。作为回报,实验者会给他们一些手指饼干。有时这些回报是相同的,有时一个孩子会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的手指饼干。即便他们还不能用言语描述这种不平等的分享行为是“不公平的”,但是当得到的手指饼干比同伴少时,孩子们的脸上还是会写满沮丧,就像所有学前班孩子家长了解的那样,孩子们并不需要被教导“得到同样数量是公平的,得到的数量少是不公平的”,这种观念似乎需要时间去学习,去计算,相反,他们似乎对不公平有着一种先天的认知。
早期的人类组织几乎都有一定的地位等级,有一些人的级别高于其他人。但是,他们没有增加相当数量财富的能力。而且当时的人口数量是以几十计而非以万计,因此社会阶级的顶端和底端之间不可能有太大差别。就像人类的灵长类亲缘动物那样,早期人类也只会比较在意自己在各自所处的小团体内的地位。早期智人(现代人的学名)的自然社会结构是一个地位阶梯,但是一把很短的梯子。
从那以后,变化的就不再是人类的本性了,而是非常实用的、具体的、晚近的——人类发明了农业。10万年间,采猎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一万年前,农业几乎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同时出现。在进化时间表上,一万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人类破天荒地能够在一个地方定居生活,种植谷物,并把收获的谷物贮存在陶罐中。人类也开始豢养家畜,从牧人的角度来看,豢养就是一种用来存储走兽的肉的工具而已。大量食物一旦被积累起来,一些人积聚的粮食比别人多的情况就成为可能。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此后不久,城市就在古埃及、古中东、古中国、古印度以及美洲的一些地区兴起了。随着这些大规模的密集的农业社会的出现,财富不平等现象开始抬头。
想要判定古代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是很难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猜测,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是相当高的。绝大多数大型古代农耕社会,都有一位国王或者其他形式的统治者,他们掌握着权势和大量财富。而在社会阶梯的低端,大部分普通人是农民,奴隶制被普遍采用。在现代历史上,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直到现在,它都是人类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最高点。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大萧条前的人类不平等峰值相当的地步。
如果人类不是唯一关心地位的物种,我们就可以声称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高的社会阶梯,使得我们灵长类亲缘动物和原始采猎者显得愈加矮小了。这些数量上的差别,为人类进化中的不平等程度和人类如今面临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别奠定了基础。
以上谈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你询问人们是否相信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他们的回答会因其自身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充满偏见。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倾向于认为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很过分了,但是那些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会说,这种体制看上去运行良好。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确定: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才算“太不平等了”?
探讨此问题的重要视角形成于1928年巴尔的摩的一户上流人家。威廉·李·罗尔斯(William Lee Rawls)七岁的儿子约翰得了白喉, [13] 这是一种与流感类似的呼吸道传染病。然而,跟流感不一样的是,儿童感染白喉的死亡率高达20%。但是,威廉的儿子能够享受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治疗,因为他父亲是当时巴尔的摩最有名的律师之一。在持续的看护下,约翰痊愈了,但是他在痊愈之前把白喉传染给了他的弟弟波比。波比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死时还不到6岁。
一年后,年幼的约翰又卧床在家,这次他染上了肺炎。后来他又痊愈了。但这回他把肺炎传染给了他两岁的弟弟汤米,同样,这个小男孩也未能幸免于难。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长大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自传中写道,两位弟弟令人心碎的离世,是他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也许他的弟弟们没有罗尔斯皮实,也有可能只是他们运气不好。罗尔斯本人不仅天生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还拥有聪明的大脑和坚定不移的自律品质。大部分人都认为以上令人钦羡的品质将帮助任何拥有这些品质的人进入精英管理型社会的顶层梯队。
然而,约翰·罗尔斯对这种观点持有深深的质疑。他诘问道,为什么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会受到如此追捧?他不过只是幸运地、碰巧地生而聪明罢了。如果他同时具备对工作的强烈信仰,也只不过是偶然中了“努力工作”特质的彩票而已。而且,如果一个男孩足够强壮,他就能够从一场恶疾中死里逃生,而一个身体羸弱的孩子则会夭折。这仅仅是生活中残忍的事实。除了在这方面给予道德上的鼓励之外,罗尔斯并不觉得有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 [14] 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被称作“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试想一下,在一次星际航行中,你从深度睡眠中被唤醒,除了你自己,你想不起任何事。你不记得自己是穷还是富,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强壮还是虚弱,聪明还是愚笨。当你的飞船驶近一个新的行星时,你需要从这个星球上的很多社会中选择自己愿意生存的社会。问题在于,你也完全不知道在你选择的社会中,你将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
继续设想下去。在这些外星球中,有些星球的不平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奴隶制是很正常的事情。其他外星球看上去虽然没那么“不平等”,但实际上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也是很高的。其中一些居民极端穷困,而有些人却相当富有。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的平等程度很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在这几类星球中,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有些勇敢者可能会选择不平等社会,并准备在这片土地上搏杀出一片天地。但罗尔斯认为,任何理性人都会选择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这样能够保证,即便出现可能的最差结果,也是可以忍受的。罗尔斯的洞见在于,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询问人们,到底怎样的不平等是“正义/非正义”的,他们的观点将因他们的能力和私利而充满偏见。最强大、最聪明、最具竞争力的个人将会倡议更加不平等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先天优势。同样,那些前景最差的人会要求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因此,与其说人们在表达他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不如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什么能为他们带来利益,什么能够完全消除对他个人所处位置的偏见。罗尔斯认为,对于“无知之幕”的窥视,将会让我们比在其他情况之下看得更加客观。
当然,“无知之幕”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一项研究已经把它应用于实际数据。 [15] 他们把人口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20%做了五等分,然后要求一个包含5000多美国人的课题组样本,预估每部分人群分别占有了美国全部财富的多大比例。虽然参与研究的人能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但他们的回应极大程度地低估了不平等的严重性。譬如,他们判断最富有的5%人口拥有整个国家59%的财富,但实际上他们占有的比例是84%。
然后,还是用这种五分法,这些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心中“理想世界”的分配方式。这个实验课题给这个序列里最富有的20%人口分配了1/3的财富总量,最贫穷的20%人口大约分到了10%的财富(实际上,最贫穷的20%人口所占的财富总量也就是0.1%)。这样理想的分配看上去并不像是美国这个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相反,这种分配方式像是在瑞典这个地球上最“平等”的国家。
这项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是研究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们画出了一对饼图,以说明两种不同的财富分配方式。参与者并不知道其中一个代表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分配情况,而另一个则是瑞典的情况。根据研究者的要求,如果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这个社会中的任何经济地位中,他们要选择哪一个饼图代表的社会是他们乐于生活其中的。换句话说,研究者把参与者置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并让他们做出选择。
令人震惊的是,92%的美国人选择了瑞典模式。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选项中达成一致的数量——无论男女,都有超过90%的人选择了瑞典模式;那些拿着6位数薪水的人,有89%的人选择了瑞典模式;年收入少于50000美元的人,有92%选择了瑞典模式。
这种共识甚至跨越了政治立场,有90%的共和党人和94%的民主党人选择了瑞典模式。在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概念之后的40年,人们仍像他预测的“理性人”那样行动。
罗尔斯运用“无知之幕”论证,一旦抛开自我利益,任何人都能看出“平等比不平等更受欢迎”。诺顿和艾瑞里的研究则证实了大部分人的确更喜欢平等。课题并没有选择完全的平等:他们仍然坚信最顶端的5%的人应该远比底端的5%占有更大的份额。但在我们面对的现实与人们对它的应然判断之间还是存在鸿沟。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之中。对于人类在过去10万年的演化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并不适用。
缓慢进化的食欲与急速变化的环境是十分不匹配的。这种不匹配是现代社会许多痛苦的根源。拿饥饿来说吧,进化并不依赖于一个机体从“我需要这些数量的卡路里才能生存”到“因此我需要食用特定的食物”来进行推理。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太复杂了,太靠不住了,而且对人类来说并非当务之急。相反,天性只是在对这种食物的品味中被构建起来的。我们对糖和脂肪这些营养物质进化出了欲望,是因为它们在增重方面有很高的效率。对于我们的采猎祖先来说,食物是极为稀缺的。因此,对饥饿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吃撑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对糖和脂肪有着贪婪欲望的早期人类,更容易打败那些对美食的欲望不太强的人。结果这种特质传遍了全人类。但是在当今世界,食物充沛,这种贪婪就导致了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疾病。天性甚至在我们的胃有饱腹感的时间和大脑得到满足信号的时间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益的延迟。这有助于确保我们的祖先每顿饭都会多吃一点。但麻烦的是,这种延迟机制到现在还在运行。
同样的“不匹配”在我们的性生活方面也造成了一场浩劫。进化并不依赖于个体制订家庭生育计划。相反,它仅仅是塑造了一些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抗拒的人。然后,它以这种方式塑造了我们——那些让我们眼珠转动、脚趾抽动的意乱情迷的行为,也是造人的行为。一方面,这个系统看上去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全球人口数量最近已经超过了70亿大关。但是想想美国全部怀孕数的一半以及80%的青少年怀孕都是意外怀孕, [16] 再想想承认存在婚外情的已婚人士占比25%的事实, [17] 我们不得不质疑石器时代的性爱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匹配度。我们的基因再生系统也许太成功了,成功到我们今天都不知想要何种生活,如果某些人只要再让人“可抗拒一点”,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很多痛苦。
同样的“错配”也存在于我们日益进化的对地位的渴望和现代经济环境之间,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高社会地位伴随着生存和再生产方面的许多利益。我们追逐地位的先贤,比他们懒散的同时代竞争者留下了更多的后代。其结果是,他们把内心深处对地位的渴望也馈赠给了我们。对许多人来说,金钱、权势和来自他者的艳羡,看上去就像食物和性爱那样难以抗拒。温顺驯服的人可能最终继承了土地,但是骄傲者直到现在仍牢牢地掌握着土地。
数十万年来,我们思想和身体的社会阶梯的演进只有几级。如果当今世界的阶梯仍停留在我们曾经习惯的人口规模上,那么我们对于地位的渴求也许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样,如果我们是那种不怎么在乎身份地位的物种,那么今天巨大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们对于高地位的内在渴求撞击了我们能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不平等巨塔。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对穷人而言的,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那些给我们的童年打上烙印的免费午餐、饭票和政府发放的奶酪都是指示我们的家庭所在的社会阶梯的客观信号。但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打饭处所感受到的那种“失去方向感”,并非基于对金钱的计算,而是我的主观感受与新的地位阶梯的现实相吻合。
当我们检视人类对社会地位的渴望时,结合世界上许多经济体近几十年变得相当不平等的事实,我们对于不平等的观点就会变化。如果我们对不平等的回应由我们对地位的需要所形塑,那么不平等就不单单是我们有多少钱的问题,也是我们与他人比较各逢所处位置的问题。就此而言,金钱只是我们继续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真穷,感觉贫穷的影响也很大。这是你对自己在地位阶梯上的主观感受揭示了你更想成为什么人的原因。
[1] N.E.Adler,E.S.Epel,G.Castellazzo,and J.R.Ickovics,“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White Women,”Health Psychology 19(2009):586-92.
[2] The health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status are described in more detail in Chapter 5.Decision making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3;work performance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8;and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beliefs in Chapter 4.
[3] M.D.Alicke and O.Govorun,“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in The Selfin Social Judgment,M.D.Alicke,D.A.Dunning,and J.I.Kreuger(eds.)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5).
[4] C.E.Preston and S.Harris,“Psychology of Drivers in Traffic Accident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9(1965):284-88.
[5] Student Descriptive Questionnaire 1976-1977,College Board,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Princeton,NJ.
[6] C.Sedikides,R.Meek,M.D.Alicke,and S.Taylor,“Behind Bars but Above the Bar:Prisoners Consider Themselves More Prosocial Than Non-Prisoner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2014):396-403.
[7] K.P.Cross,“Not Can,but Will College Teaching Be Improved?,”New Directionsfor Higher Education(1977):1-15.
[8] E.Pronin,D.Y.Lin,and L.Ross,“The Bias Blind Spot:Perceptions of Bias in Self Versus Other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2002):369-81.
[9] R.O.Deaner,A.V.Khera,and M.L.Platt,“Monkeys Pay Per View:Adaptive Valuation of Social Images by Rhesus Macaques,”Current Biology 15(2005):543-48.
[10] R.A.Gibbs et al.,“Evolutionary and Biomedical Insights from the Rhesus Macaque Genome,”Science 316(2007):222-34.
[11] C.Boehm,Hierarchy in the Forest: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2] S.F.Brosnan and F.B.De Waal,“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Nature 425(2003):297-99.
[13] T.W.M.Pogge,John Rawls:His Life and Theory ofJustice,M.Kosch,tr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4] 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revised edition,1999).
[15] M.I.Norton and D.Ariely,“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One Wealth Quintile at a Time,”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2011):9-12.
[16] “Trends in Teen Pregnancy and Childbearing,”June 2,2016,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www.hhs.gov/ash/oah/adolescent-health-topics/reproductive-health/teen-pregnancy/trends.html.
[17] A.J.Blow and K.Hartnett,“Infidelity in Committed Relationships II:A Substantive Review,”Journal of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1(2005):217-33.
莫莉·奥尔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从未想过划定一条把有产者和无产者区分开来的官方线。 [1] 实际上,她本人就在这条线以下的一边长大,她们六姐妹住在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六个人分三张床。她是这个乌克兰移民家庭中第一个完成高中教育并顺利升入大学的人。她在一家鲜为人知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她从未指望这篇文章中手工计算的数列有朝一日会定义几百万人关于“多少是够”的奇特概念。
在20世纪60年代,奥尔桑斯基在社会保障局从事研究工作。她的日常工作是从调查数据中寻找定义贫困的更优解。在她之前,由于没有测量尺度,很难确定美国到底有多少穷人。奥尔桑斯基想要基于家庭在食物上的花费来划分家庭的贫困程度。她了解到,当时的普通家庭平均有三分之一的钱花在食物上。她的这种想法产生于农业部当时刚出台的四个“家庭食品计划”之后,其中每一个计划都描述了家庭所需的一种健康饮食的固定供应情况。这些计划的制订横跨最高家庭生存成本(慷慨食品计划)和最低家庭生存成本(节俭食品计划)。因此,奥尔桑斯基在一篇写于1963年的论文中,假设研究者可能通过“第二等级”(低支出水平)的食品计划和将其家庭食品支出的数量乘以三倍的方法来定义贫困。在这个框架下,“多少是够”的钱数被定义为够全家吃饭的钱和其他最基本的花销,在此数字以下的收入被认为是“在贫困线以下”的收入。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困开战”。由于缺少界定贫困者的官方衡量尺度,政府决定采纳“奥尔桑斯基指数”确定谁有资格拿到政府救济金。莫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震惊。虽然她为了帮助研究者衡量贫困,已经对自己提出的方法做了改良,但她从未想要将这一方法用于决定谁该领到救济金。尽管她支持以“低收入者食品计划”作为“奥尔桑斯基指数”的基础,但政府却想把“节俭食品计划”当作基础。作为回应,她试着给预算做一些填充,譬如建议每天15美分的附加预算,包括对儿童的特殊照顾,或者是加一杯咖啡等。从她对预算的修修补补中,你能看到一个曾经与贫困为伍的人的痕迹。她曾说:“当我为贫困而写作时,我无须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只需有良好的记忆力即可。”然而,她的上司最终否决了她的建议并选择了最便宜的食品计划——“节俭食品计划”,以三倍于“最低养家支出”划定了官方贫困线。
同样的公式依然是如今美国政府定义贫困的方法。这个指数根据通胀情况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因为家庭消费种类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变化影响颇大。举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家庭在食物上花费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另外三分之二则用来支付食物以外的一些花销。然而在今天,美国人平均花在食物上的钱大约只有其总收入的13%。现在要想让贫困线有着同它刚被发明时相同的含义,你就需要把最少的食物花费乘以8,而不是乘以3了。
如今,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无论这个家庭是生活在纽约还是生活在堪萨斯州的乡村公路边,贫困线都是23850美元。然而,当2013年盖洛普的一项民意测验要求美国人说出他们心目中能“让一个四口之家生存下去的最少收入”时,回答的平均数是58000美元。 [2] 他们的回答与其自身的收入相关。家庭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人认为生存下去需要44000美元,但是家庭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人则认为,至少需要69000美元才能生存。当盖洛普提出有多少钱才能称得上“富裕”的问题时,回答的中位数则是150000美元。这个回答同样取决于回答者自身的收入情况。一个人挣的钱越多,他认为的“富裕”标准就越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富裕”一般等同于其真实收入的3倍。
谁才是真正的穷人呢?谁又不是真正的贫困?这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一项政府调查声称,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中,有96%的家庭有电视,93%的家庭有微波炉,83%的家庭有空调,81%的家庭有移动电话。 [3] 一个刷着手机、用微波炉热饭、看着电视飞速换台的家庭,真的能被称为“贫困家庭”吗?
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他修建了蒙蒂塞洛庄园——在他所处时代最赫赫有名的府邸。蒙蒂塞洛闻名天下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其建筑,也因为其中各种领先于时代的小装置。这些小装置很多都是杰斐逊自己发明的。譬如,杰斐逊家中办公室的“测谎仪”(polygraph)。它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测谎仪”,而是一个装有信纸和连接在一系列木质杠杆上的两支钢笔的机械新玩意儿。当你用其中一支笔在信纸上写字时,另一支笔同时就能写好一份副本。蒙蒂塞洛还有一些小型升降机,它们是由一组滑轮运行的小型电梯,用来跨楼层送餐。还有杰斐逊的“大钟”,它复杂的齿轮不仅可以报时,还可以显示日期和月份。
除了这些“机械奇迹”之外,杰斐逊家没有热水,没有空调系统,没有电,也没有微波炉。从物质标准来看,他被认为比今天许多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更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他是贫穷的呢?因为历史的视角表明,贫穷和富有总是相对于在特定的时空下其他人拥有什么而定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清楚地论述了这一点 [4] :
我之所谓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说来,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但是,到现在,通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佣劳动者,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习俗,又以同样的方法,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生活上的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或女人,没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 [01]
当年的亚麻衬衫就像今天的移动电话一样。两百多年前,经济学之父以其推理方式得出的结论,如今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了。贫穷和富有并不仅仅跟金钱的绝对数量有关。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穷人并不是真的在挨饿,问题的关键是相对地位。为了理解事情之所以如此的理路,我们必须检视人类思维评判价值的最基本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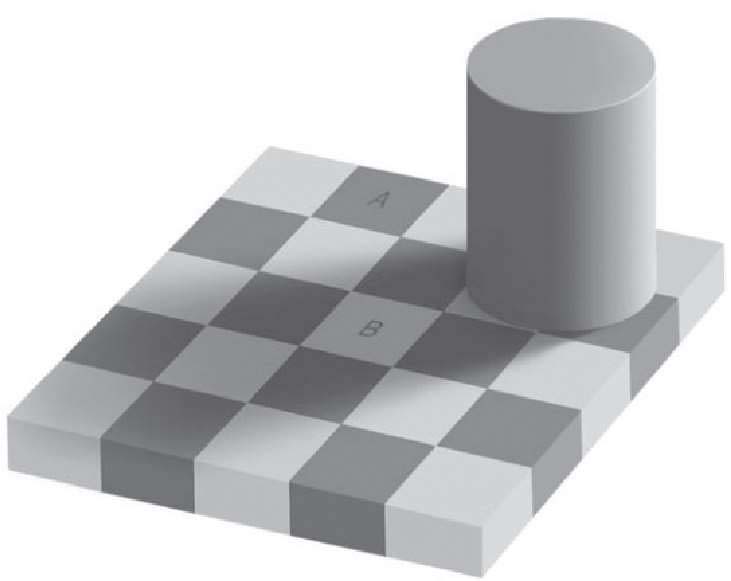
图2.1 棋盘幻影
让我们看看图2.1的棋盘格瓷砖。也许我不可能使你信服:打上A标签的灰格子与打上B标签的格子的亮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的亮度确实是一样的。用眼球盯着看上好几分钟,随你如何倾斜,如何眯着眼看,你还是不能使幻觉消失。你的大脑确实在运行着一个良好的视觉系统应该具备的功能,那就是结合情境考虑问题。因为你的大脑知道,物体在阴影下会比在亮处看起来更暗一些,它抵消掉了这个圆柱体投射的阴影,似乎在说:“如果B在阴影下看起来还亮一些的话,那么它在现实中一定是更亮的。”
心理学家被视觉的幻影吸引的原因在于,它们让我们通过体验在自己了解的真相和事物看上去的样子之间的冲突,捕捉到大脑思维小伎俩的灵光乍现,发现自己曾经没有注意到的现象。在“棋盘幻影”这个例子中,我们的感知是有偏差的,而且我们犯了错误。但是偏差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在阴影下看起来就是更暗一些。因此,一个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视觉系统可以使我们适应野外观察,赋予我们在野外更准确地感知事物的能力。
对情境的依赖不仅仅适用于视觉,它也是我们的大脑观察任何事物的主要途径。回想一下我们的饥饿感。知道什么时候要吃东西,什么时候吃饱是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之一。它说明我们已经进化出敏感的热量测量机能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并不尽然。我们对于饥饿和饱腹的感觉,相当程度上是受环境影响的。
在一个盘子里面堆满肋骨,就像我们最喜欢的“小猪”烧烤连锁店里那样。然后,在用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要求其中一个用餐者评估一下他吃得有多饱,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半饱”的估计。现在,你再拿两根小肋骨,以高级餐厅的服务方式,把它们放在盘子正中,或者把它们垂直搭起来,摆上几片小绿叶。然后同样在用餐过程中询问用餐者,他感觉吃得有多饱,他的回答会跟在烧烤店中的回答一样,觉得自己吃了半饱,即便实际上他吃得比在连锁烧烤店要少得多。
人们判断自己吃得有多饱,不仅仅根据他们摄入了多少卡路里。对此最简明的证明来自康奈尔大学布莱恩·万斯克(Brian Wansink)领衔的研究。他的团队给一些碗做了手脚, [5] 用一根固定在汤碗底部的管子连接桌面和一大锅西红柿汤。当用餐者吃饭的时候,更多的汤会不知不觉地通过管子流进碗里,使碗里的汤一直保持着同样的量。奥利弗·加尔东(Oliver Gardon)声称有一个永不枯竭的“通心粉碗”,但是万斯克的实验室发明了真正的“无底洞汤碗”。
用“无底洞汤碗”喝汤的两人,即便吃了差不多用普通碗的人的两倍,却坚信自己与其他人吃的量差不多。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两组人的饱腹感竟然相同。他们的饱腹感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吃了多少的感觉,而不是根据他们实际消耗的卡路里。而他们对自己吃了多少的感知,又取决于他们使用的碗的大小。
一天晚上,我打开冰箱拿牛奶。出于某种原因,我一下子把半空的1加仑装牛奶盒撞到了冰箱顶上,由于用力过猛,我的手受伤了。听到这声巨响后,我的女儿也从另外一间屋子里跑了过来。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她试图解释我的行为:“当你拿起牛奶盒时,其实你想要的是更多的牛奶。”即使我并非有意识地考虑牛奶盒中的牛奶到底有多重,但是当时的我一定期待着拿到一满盒牛奶,因为这正是我的手臂肌肉准备好拿起它的力量。
很多研究显示,预期和情境影响我们对重量的感知。如果你刚刚抬了一大袋货物,而不是拿了一块棉花糖,那么你会觉得1加仑牛奶比它实际的重量要轻得多。这种对重量的相对判断已被多次证明。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已经被认为是大脑如何把原始的感官数据(譬如肌肉紧张等)转化为主观的重量感觉的基本法则。然后,后来的一项研究,让所有人重新思考了他们的猜想。
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他当时主导了一项实验, [6] 实验主体类似于先前成百上千的展示“感官判断是相对的”实验。他按照重量把一些小铜块排成一列,然后要求参与者拿起这些小铜块,并描述“很轻”或是“太重”;接着再拿起一块轻一点的,后者会通过对比而显得更轻。当他们先拿起轻的,然后再搬重的,那么重的那件就会让人觉得更重。
然后,当实验进行到一半时,布朗暗中要求参与者拿起一盘很重的东西,然后放到一边,以便于他们能继续判断下一组物体的重量。这个载重的盘子本身就很重,但当他们拿起下一个重物时,之前举起盘子的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对重量的判断。为什么举起单一的重物会影响人对重量的感觉,而举起一组重物的时候就不会呢?
如果相对效果是一条不会改变的心理学法则,而这条法则又能够统领肌肉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对重量的感觉,那么这个悖论就不会发生了。我们所做的比较相比于我们通常猜想的要更复杂,这是一条早期线索。我们不仅进行持续不断的比较,还对哪些比较算数、哪些比较不算数进行了细致的推测。
我们十分习惯于判断社会地位,这一能力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骑自行车或有了几年驾龄的老司机那样轻车熟路。当我在写作本章内容的时候,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坐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坐在我周围的是这座大学城里各式各样的居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银发男人戴着玳瑁眼镜,按扣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拉链毛衣。他与他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孩子们穿着T恤衫,戴着棒球帽,有时会不自主地流露出一股自信的派头。还有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穿着一件套头衫,“北面”的徽标在衣服上最显眼的位置闪亮着。他一直在看他的手机。一位身着紧身牛仔裤和毛衣的美丽女子把太阳镜架在她干净利落的头发上,她的耳饰与项链是配套的。在他们旁边,一对稍微年长些的,应该也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情侣相互依偎,亲密地交谈着。情侣中的女士围着一条彩色图案的披肩,她凌乱的金发披散在颈边,披肩下面是另一种花色的毛衣。男士穿着一件蓝色的法兰绒衬衣,有着一头柔软卷曲的头发和胡须。他们好像刚从被窝里爬起来不久似的。
如果你走进任何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看上去最直接的任务就是猜测大家的社会阶层。这似乎是一项需要多年才能掌握的技能,但也可能不是这样。有一天,我三岁的女儿指着挂在我家墙上她所在的全日制托儿所的班级合影,郑重其事地宣布:“艾莉跟我差不多富有!”我被她的宣言给惊到了,于是指着照片上另外一个孩子问:“那她怎么样呢?”我女儿回答道:“哦,她很穷的。”
现在我被弄糊涂了。我女儿是在我任教的大学开办的全日制托儿所上学。能来这个托儿所的孩子家长,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所大学有关系。在三年的接送、玩耍和生日会后,我对她们班成员的家庭情况应该说是充分了解的,并且知道班上所有父母的工作职位。他们中很多人是教授、医生,其他的人也是刚毕业的学生或是学校的工作人员。
我把女儿的注意力再次引回班级照片上,照片里的15个孩子都被她贴上了标签。父母是教授或医生的,她就说他们是“富有”的;父母是刚毕业的学生或是校工的,她就说他们“贫穷”。客观来讲,根据奥尔桑斯基指数,班级里的家庭没有一个会被划到“穷人”那一边去。但是我女儿相对于自己的情况和她的教授父母做出判断,并以此为标准,她在贯彻这个标准的准确性方面堪称完美。她只是个例吗?并不见得。保持15次随机猜测都准确的可能性是十万分之三。我产生了一种交织着骄傲与羞愧的奇怪感觉。我的女儿特别精明吗?还是她不自觉地沉浸于地位之中?事实上,她可能两样都不是。研究表明,判定其他人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确是大部分孩子的游戏。
心理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和达彻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通过邀请53对互不相识的大学生进行5分钟对话,来测试成年人对社会地位判断的准确性。 [7] 研究者对这些对话做了录音(让我们把这些参与者称作“聊天者”)。然后,他们给另外成对的参与者展示每段录音中为时一分钟的小片段,这对参与者需要根据录音内容猜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并把他们放在我们曾在图1中见过的那种“地位阶梯”上(我们称这些参与者为“评分者”)。
在监测了这种行为的一小部分样本之后,“评分者”对“聊天者”的印象就相当准确了:他们对“聊天者”在“社会阶梯”上的评级与“聊天者”自我陈述时透露的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明显相关。研究者解码了录音带,以观察聊天者在交流他们的阶级差别时显示的个人特质。他们发现,比较富有的聊天者在对话中的参与度较低,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打扮自己,乱写乱画,摆弄钢笔或者其他小物件上。相反,相对比较贫穷的“聊天者”的参与度较高,他们直视聊天伙伴,点头和微笑的次数也更多。更高的地位意味着较富有的参与者在这段对话中没有什么可聊的,没必要让别人接受和喜欢自己。相反,相对较穷的参与者会更加努力地希望自己被人接受,被人喜欢。
像克劳斯所做的这种研究显示,只需要很少的信息,社会地位就能很快地被直觉感知到。但另一种形式的研究指出,事实上,人们无须借助任何有意识的行为,就能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进行社会比较。其中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可靠的发现是,如果你特别留意并考量一个在某些方面明显强于你的人,相比于你从未在此人身上花费任何心思而言,会让你对自己的感觉更糟。同样,如果你同自己觉得在某些方面次于你的人做比较,也许会让你好过一点。由托马斯·穆斯魏勒(Thomas Mussweiler)领衔的心理学家团队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样的社会比较效应是否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 [8]
调查者要求研究参与者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评估自己的运动能力:你能做几个俯卧撑?你跑百米冲刺需要花多少时间?但是在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参与者被要求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展示他们的运动能力,同时开启一台内置一串随机字母的电脑监测仪。参与者不知道的是,字符串每15/1000秒就会被一位名人的名字替换,在这一分钟内,这个名字大概出现10次。在此期间,这个名字不会被意识察觉到,因此它产生的任何效果都是很细微的。
其中一组参与者接触的名字是“迈克尔·乔丹”,另一组接触的则是“约翰·保罗教皇”,穆斯魏勒假设,人们会认为教皇的运动能力逊于篮球明星。不出所料,下意识地接触“教皇”的人对自己运动能力的评估要比下意识接触乔丹的人高。无论如何,得到这个效果的比较过程,一定是产生于下意识的。因为参与者在比较自身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阅读了这些名字。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研究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一分钟,你正坐在路边的咖啡厅,怡然自得地享受一杯咖啡,浏览一份杂志。你开始思索:“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我算得上成功吗?我敢打赌,谢莉尔在办公室努力工作取得的成就一定比我多。我应该用硬木装修厨房吗?”尽管这些想法看上去不着边际,但它们通常是意识处理后的结果。正如上文提到的迈克尔·乔丹的例子,当你翻阅杂志的时候,你也许已经潜在地受蒂凡尼广告的影响,即便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也许当你正在搅拌方糖的时候,你在意识中就已经开上了身边疾驰而过的保时捷。
即便情境可以影响你对明暗的感觉,就像“棋盘幻影”那样,你也不会怀疑你面前的杂志页的白或者墨水的黑。你不会怀疑杂志纸张的重量,即便你举起椅子和举起咖啡杯之后对纸张重量的感觉会不同。你不会怀疑自己还想要一杯咖啡的直觉,尽管这种渴望也许是由你的马克杯的尺寸所赋予的。“这是黑,那是白;我还想要一杯咖啡,一个升级的厨房。”我们意识到这些想法和情感,它们是大脑计算的结果,但是我们对于无意识的计算本身依然一无所知,因为大脑总在持续不断地监测环境,做比较,并直接给出结果。于是,我们在根本没有意识到比较的情况下,依然会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
有一个线索能证明你已经无意识地把自己与他人进行了比较,你发现自己在一些对你不太重要的事情上比较有竞争力。每逢星期三,我和我的六位专家同事在教堂山的一间小会议室,这间会议室里有两堆牌,还有一个粉刷过的、装着许多巧克力的木头南瓜。我们一起吃午餐,玩着“哦上帝”(Oh Hell)的纸牌游戏,并讨论当天的热点事件——有时是关于部门业务的正经事,有时则是津津有味的绯闻。有些日子,屋子里一片寂静。我们的眼睛在牌局之间游移,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
我们玩的时候没有用钱,大家不会有实际的经济损失。事实上,“胜利”几乎可以被忽略。因为当游戏结束时,赢家必须忍受学生们疑惑的眼光,把粉刷过的南瓜扛下大厅,放回原位。
但游戏总是扣人心弦的,没有人能抗拒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机会,即便只有一个小时,即便用的是最愚蠢的方法。尽管玩这个游戏并没有涉及经济收益,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们还要投身于如此紧张的竞争之中呢?因为对大脑来说,金钱和相对地位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处理两者用的是大脑的同一片区域,我们有时把它称为“报酬回路”。“报酬回路”是一片具有内在联系的大脑区域,当我们得到了或者马上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这个区域的神经元就会被触发。“报酬”的表述来自一项对老鼠的研究。把一只饥饿的老鼠关在笼子里,它每次用爪子按下一个按钮的时候,就会得到一小块食物,不久,它就像按老虎机那样按压着按钮。
如果正好有一个有线的内置器,通过这只老鼠的头盖骨,进入它脑中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个内置器就能记录这个过程中从老鼠的大脑神经元传来的电子脉冲。如果你把这条电线连接到一名说话者身上,那么你就能听见神经元咔嚓、吱啦、砰砰的声音,就像无线电的静电干扰那样。一开始,这种声音比较低沉和稀少,但是当老鼠把它的爪子伸向按钮,“报酬”开始出现时,噪音就会渐强。一旦小块食物被吃光,这种声音就又会慢慢消失。“报酬”的吱啦声越强烈,老鼠就会更急切地再一次按下按钮。
在“报酬回路”的电子活动和“请给我更多”的回应之间的强联系,给了麦吉尔大学神经学家詹姆斯·奥德和彼得·米纳一个独创性的灵感。 [9] 这个食物回馈实验看上去有一个闭环——按压按钮,小块食物出现,报酬中心被触发,动物开始更频繁地按压按钮。解释这个闭环的一种说法是把大脑的电路活动,当成是确保过去成功的按压按钮会被重复的一种方法。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它意味着按压按钮和吃食物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大脑自我刺激的方式。换句话说,也许在这个部位的大脑刺激是自我回馈的,吃只是触发这种回报的方式。
奥德和米纳追问,如果把食物激励全部拿走,取而代之的是把按钮与电池直接连接起来,让电流直接刺激老鼠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老鼠强迫性地按压按钮。在实验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它们不仅为了坚持按压按钮而放弃了食物和水,而且忍受着脚疼穿越带电的地板,以求走到按钮旁。电流刺激在为它们的大脑提供回馈信号方面十分有效,以至于老鼠们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了需求。它们会持续按压这个按钮,直到精疲力竭,崩溃为止。
如果你觉得这种大脑刺激装置很好玩,有机会你也想尝试一下,那么我还是奉劝你打消这个念头:让你自己免于脑部手术,去喝杯啤酒吧!“报酬回路”的大脑通路进化到了让人类持续寻求对生存和再生产有利的事物——像食物和性那样的东西。但是,所有让人们情绪亢奋的物质,从黑比诺到强效可卡因,刺激的都是同一块大脑网络,因为这些刺激性物质有着与构成大脑报酬回路的化学物质相似的化学结构——当你在小酌几杯时,你正在接受与奥德和米纳的老鼠被电击时的化学结果。
当然,要研究人类,我们不需要通过内置于大脑中的线路听其噪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功能性MRI(磁共振成像)扫描得出的彩色大脑扫描图,如果你在人们吃巧克力、享用马丁尼,或者是(非常尴尬地)进行性生活时观察这些大脑扫描图,你会看到同样的“报酬回路”在嗡嗡作响,因为是同样的大脑网络在回应所有种类各异的经验,报酬网络在许多不同种类的刺激之间创造了一种“共同货币” [10] 。你可能并不感到奇怪,你在赚钱时也会有相同的反应。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当研究参与者在做出赌博、选股等经济决策,或者为了这些经济决策去挣钱的时候,报酬回路的表现就会与它在面对食物、性或者毒品时一样。
然而,一个奇怪的发现是,报酬回路对相对地位的反应与对实际金钱的反应一样强烈。 [11] 让我们来看看脑神经科学家克劳斯·弗里斯巴赫(Klaus Fliessbach)领衔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志愿者捉对玩耍一个简单的游戏,在玩游戏时,他们的大脑会被扫描。在每轮游戏中,参与者需要识别类似的两张图片上哪张的小圆点更多,但他们没有时间数这些圆点。因此他们需要快速估计,当他们识别正确的时候就会赢钱;每轮识别之后,电脑都会显示每个队员所赢的钱数。
在这个研究中,真正的问题在于,“报酬回路”是否真的“关心”相对地位,这也的确是关键问题。抛开游戏参与者挣得的金钱数量,“报酬回路”在参与者挣的钱数比其他参与者多的时候,更加活跃。单是知道自己比其他参与者玩得好这件事本身,就能引起与性、金钱和毒品类似的大脑反应。地位显然是一个有力的驱动器。类似这种实验表明:当我们说人们追求地位时,“欲求”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毫不费力地就能通过相对比较来判断由低到高的社会阶级;把这些方面放在一起考察,你就发现一个对物质财富和不平等本身难以置信地敏感的物种背后的逻辑。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当谈到一些基本的事物,譬如食物时,胃和大脑并不能准确地判断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吃饱。而一些更加抽象的判断,比如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一间足够大的房子,一辆足够好的车,一定是更多地取决于相对状况和比较,因为我们对这类财富的渴求并不灵敏,不能直接地感知这些嗜好。那么,我们如何在有关“地位”的日常生活中判断什么是“足够”呢?
在一项如今非常著名的决定到底多少钱才是“足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和安德鲁·奥斯华德(Andrew Oswald)从5000多个英国家庭中提取数据并进行分析。这项研究由一组与被调查家庭总体的工作满意度、报酬满意度有关的问题构成。这些数据中也包括与每位参与者的职业、工作、工作年限和每周工作时间等有关的具体信息。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把工作当成一件可以用来买卖的商品,根据供求法则确定这件商品的具体价格。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典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预测。它声称人们在挣到更多的钱时会更满足,即便要占用更多的工作时间。但奇怪的是,当克拉克和奥斯华德在分析收入和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时,挣钱最多的那5%的人竟然比挣钱最少的那5%的人还要少一些满足感,而且工作的小时数对他们的满足程度没有多少影响,上文提到的经济学理论预测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人们在拿到更多薪水时会感到更不满足呢? [12]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你爬上一级阶梯,你的比较对象就发生了变化。伯特兰·罗素说:“乞丐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嫉妒更成功的乞丐。”如果你是挣钱最多的那5%中的一员,你可能会去比较的人就没有上限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家庭医生,这样的年收入绝不算少,但是当你把自己与一个年薪百万的脑科医生放在一起衡量时,你也许就会感到不满足了。显然,这种相对比较对满足感的影响还是完胜冷冰冰的现金。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经济学家观察了在类似工作岗位的人与他人收入进行比较的情况。他们采用了一个大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记录了不同工作岗位的平均工资水平。举例来说,经济学家在考量一个45岁而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实验室工程师的相对工资时,会查找同龄/同等教育程度的实验室工程师的平均收入。他们发现,相对收入对满足感有相当大的影响。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很少起作用,跟工作时间也没什么关系。那些比同侪收入高的人满足感更强。
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实验已经证明了相对收入的重要性。使用经济数据衡量满意度是评估人们认为的“足够”的社会比较效应中最直接的手段之一。但是,相对差距效应会在满足感的主观感受之外产生负面影响。贫穷和富有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贫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社区,并让我们的孩子上一个比较优裕的学区。
如果相对比较如我声称的那样重要,那么一些奇怪的后果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大脑视相对比较为最基本的感知,那么这一定也与富足程度有关。而且,如果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由这种相对比较所调节,那么我们身边的不平等程度——不仅仅是我们的实际财富——一定会在我们生活中与贫富相关的每个领域起到关键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它也确实起到了这种关键作用。
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金森和凯特·皮凯特梳理了大量医学文献, [13] 试图寻找财富和一系列社会痼疾的关系,这些社会痼疾包括谋杀与暴力犯罪、学校成绩与辍学率、青少年生育、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肥胖、大脑疾病等,确切地讲,这类问题在穷人之中尤为严重。他们比较了有数据可查的所有富国中此类问题的比例,其发现令人震惊。
如果我们考察世界上所有国家,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平均收入与预期寿命同对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易感性紧密相关。像莫桑比克这种极度贫困的国家,就比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要糟糕得多。当你只把目光聚焦于发达国家的时候,比如西欧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个相关性就会被打破,一旦人们富有到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时,额外收入并不能保障他们从低生活质量中解脱出来。
让我们再来看看谋杀率。由于我们通常把这些社会问题看作贫困带来的问题,那么显然,暴力犯罪应该在不怎么富足的国家里更多一些。譬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些国家每人的平均年收入在20000美元左右。而在美国、挪威、加拿大这样的富裕国家,暴力犯罪率应该更低些,因为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比前者要高得多。事实上,平均收入和谋杀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预期寿命也是如此。其实,在威金森和皮凯特分析的10种社会和健康问题中,只有两种——教育成就和邻里信任——与收入有一定的关系。当这10种测量方式被加权平均到一个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总指数中去时,就与收入毫无关系了。就像你在图2.2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国家的情况呈模糊的云状,没有清晰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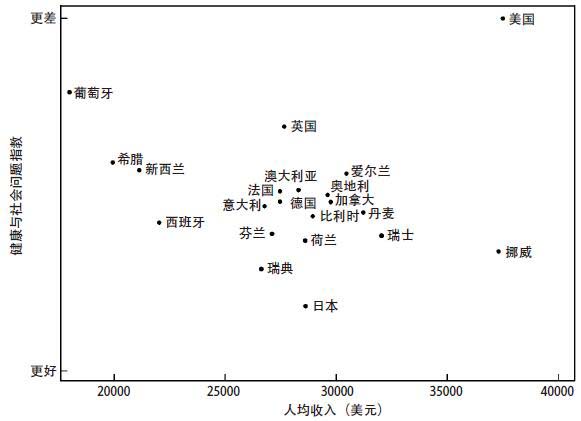
图2.2 在发达国家,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并没有和平均收入紧密相关
资料来源:根据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9)改编。
图2.2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有三个国家的位阶比其他国家高——美国、英国和葡萄牙——尽管它们分别是高、中、低平均收入的国家。在图2.2的底部,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的镜像——瑞典、日本和挪威。尽管这三个国家的收入范围差距很大,但它们的社会问题都相当少。显然,这个模型质疑了声称“贫穷导致社会问题”或者“性格缺陷导致社会问题和贫困”的简单理论。
威金森和皮凯特接着以另一种方式观察这些数据。他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将社会问题指数与平均收入挂钩,而是将社会问题指数与收入不平等挂钩。某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用该国流向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除以该国流向最贫穷的20%的人的收入衡量的。对于瑞典和日本这种最“平等”的国家,这个比率大约是4。这意味着该国最富有的5%的人挣得的收入4倍于最贫穷的5%的人挣得的收入。对于美国和葡萄牙这种很“不平等”的国家,这个比率在8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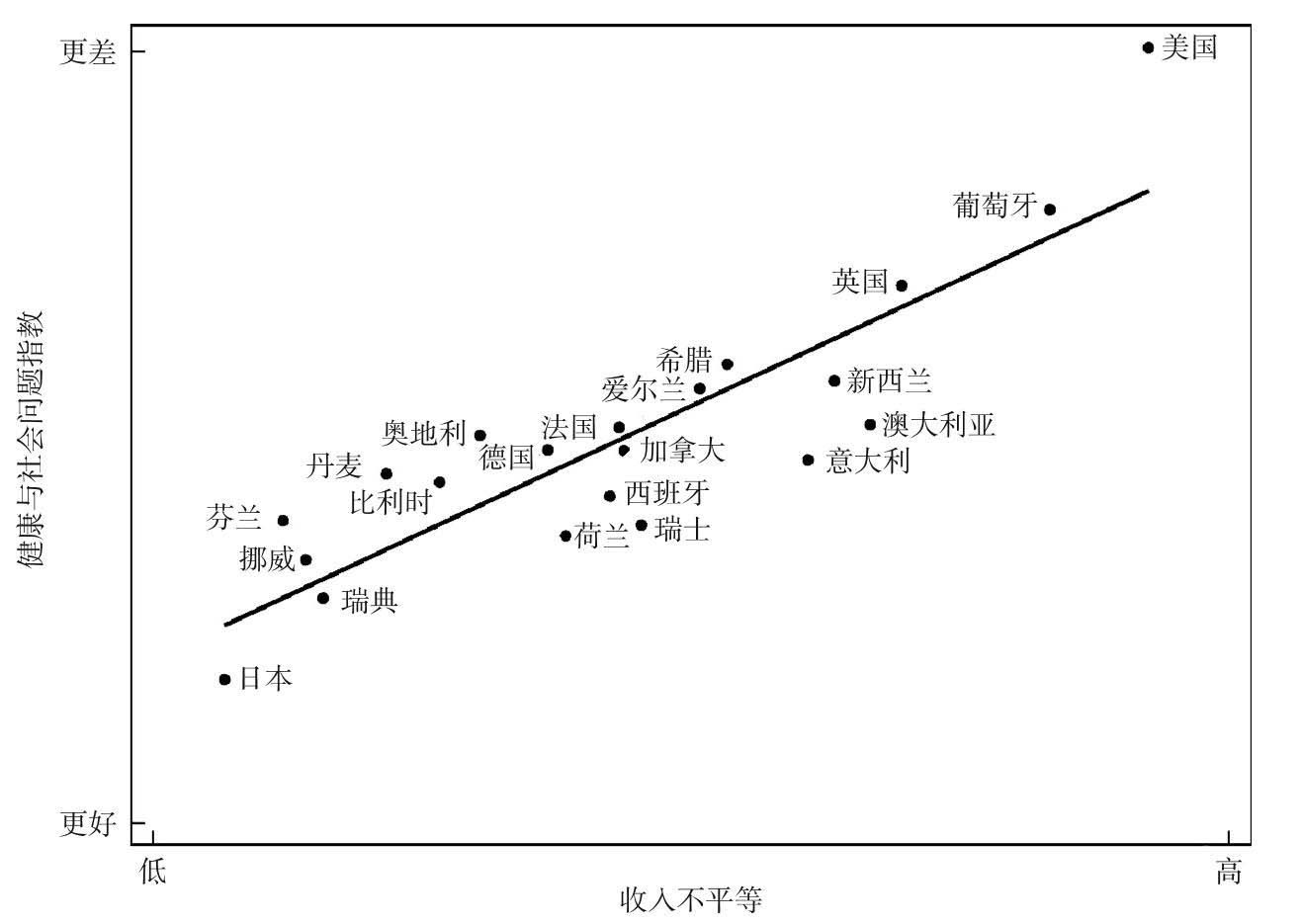
图2.3 在发达国家,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和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
资料来源:根据Wilkinson and Pickett(2009)改编。
当你从这个角度再来检视这些数据的时候,如图2.3所示,这些国家的指数就与威金森和皮凯特的预测相当吻合了。瑞典、日本和挪威不再是一个数据点的大杂烩,而是在底部左侧与最低程度的不平等和最低层次的健康与社会问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芬兰、丹麦和比利时等国沿着不平等的道路迈出一步,你就在社会问题指数的梯子上爬上了一级。当你达到最不平等国家——英国、葡萄牙和美国——它们也不再是离群数据,而是恰好落在你期望的,与其不平等程度相对应的位置上。在构成这个指数的所有10个主题之间,不平等的相关性都是很强的,而且,即使研究者从数据上掌握了每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它们之间的连接也能原封不动地保留。
也许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府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不能在它们之间进行直接的比较,就像直接比较美国的50个州那样。威金森和皮凯特强调了这种担心,如图2.4所示。图中再次出现了更不平等的地区有着更高比率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再次出现了不平等比平均收入有更大的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图2.4中,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富裕州会与亚拉巴马这样的贫困州挤在一起,像艾奥瓦和犹他这样的贫困州会与新罕布什尔这样的富裕州划在一组,即使在单一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也超过了收入。
我们通常认为,构成“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的议题的原因是贫穷。但是这些不平等效应在我们调整了收入之后仍然存在。因此,对于一个收入平平的人来说,生活在一个更不平等的地区仍然会把自己置于生活问题的高风险之下。换句话说,一个生活在高度不平等的得克萨斯州的中产阶级人士,将会比生活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艾奥瓦州的中产阶级人士更有可能遭受健康和社会疾病。
试想一下,你想要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大部分人会选择一个低犯罪率、有优质学校、邻居可信赖的社区。辨别这种社区的方法之一是做大量的数据勘察工作,在网上搜索学校考试分数和犯罪数据等信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查询当地的基尼系数,该系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常用方法。大部分大都市的基尼系数都是可以在网上查到的。颇为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如何反映特定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比较准地把握贫困和富裕的状况,或者说它们看上去的状况,无论修剪过的草坪和富有郊区绵延的房子,还是破旧的店面和衰落的城市社区坑洼不平的街道,或是生锈的家庭拖车和污染某个贫困乡村的废弃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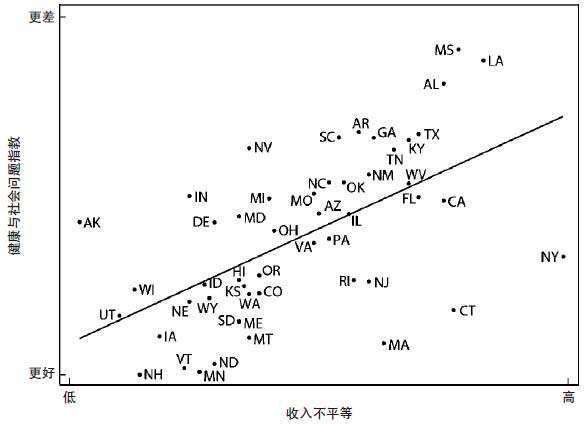
图2.4 在美国,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和收入不平等呈强相关
注:亚拉巴马AL、阿拉斯加AK、亚利桑那AZ、阿肯色AR、加利福尼亚CA、科罗拉多CO、康涅狄格CT、特拉华DE、佛罗里达FL、佐治亚GA、夏威夷HI、爱达荷ID、伊利诺伊IL、印第安纳IN、艾奥瓦IA、堪萨斯KS、肯塔基KY、路易斯安那LA、缅因ME、马里兰MD、马萨诸塞MA、密歇根MI、明尼苏达MN、密西西比MS、密苏里MO、蒙大拿MT、内布拉斯加NE、内华达NV、新罕布什尔NH、新泽西NJ、新墨西哥NM、纽约NY、北卡罗来纳NC、北达科他ND、俄亥俄OH、俄克拉何马OK、俄勒冈OR、宾夕法尼亚PA、罗得岛RI、南卡罗来纳SC、南达科他SD、田纳西TN、得克萨斯TX、犹他UT、佛蒙特VT、弗吉尼亚VA、华盛顿WA、西弗吉尼亚WV、威斯康星WI、怀俄明WY
资料来源:根据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9)改编。
不平等是很难被观察的。在那些极度不平等的地区,修剪过的草坪和废弃的门面同时存在,它们之间常常只隔几个街区而已。在我们的脑海里,似乎没有一个单独的影像代表着不平等,因为它本质上缺失单独分享的经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种共享空间的缺失,因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会把彼此的生活地点、工作地点和上学地点分开。
我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搬到北卡罗来纳。我和妻子从达勒姆开始寻找住处的时候,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城市有数百万棵树。这些树把这座城市的一切笼罩在林冠之下,白天处处阴凉,晚上漆黑一片。道路和花园看上去是从一片茂密的森林中适度修剪出来的,这些森林似乎希望自己一有机会就被翻修。然而,比这座城市美丽的树木更令人震惊的,是它的极端性。
驾车穿越达勒姆时,我们经过了一个百万富豪的社区。这个社区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依然保持着它旧有的风貌。木兰和柠檬树装点着这里的草坪。穿过一条街后,这些令人惊叹的房子就不见了。我们发现旁边是一栋砖混公寓楼,它的前侧围绕着灰暗的金属栏杆防火梯。换洗的衣物挂在窗前,男人们正在街上修车。又过了几个街区,我们置身于一片玻璃幕墙办公大楼之中,其中夹杂着几栋古雅别致的红砖楼。它们曾经是烟草公司的仓库,但早就被改成了砖块外露、有木头护栏的厂房公寓。再走几个街区,街道两旁出现了顶部是铁丝网的链条栅栏。年轻人在街角闲逛,他们的旁边就是一个社区中心,墙上张贴着“不要在街角游荡”的告示。
达勒姆地区的犯罪率相对较高。它的公立学校在低分数和高辍学率之中挣扎。我猜想,达勒姆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城市。但事实上,它的平均收入比哥伦布还要高一点。两座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达勒姆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这里是很多贫苦人士的家园,但百万富翁也更多。而在哥伦布,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没有。当然,这里的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好,但它不会给你一种鞭挞的感觉,就好像你在跨越几个街区的过程中就穿越了几个城市和几个世纪。
我们入住的民宿,位于达勒姆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我们在这里看租房广告。这家民宿的主人是一对友善的夫妻,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他们对自己精心修缮的房子感到非常骄傲。男主人是达勒姆的警员。由于他对这座城市有着颇具专业深度的了解,我们向他咨询了我们正在考虑的地方。他强烈表示并多次强调:“你们绝不会想要住到那里去的。”听到他如此谨慎,还真是让人感到不安。我向这位民宿主人最后询问了一个地址。我确信他会对此感到乐观,因为它实际上就在他可爱的房子附近的街角。他看着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然后开了口:“那房子有前门和后门,但前门最好在晚上开着灯。如果你想在天黑之后出门,一定要上好门锁。”
此时,我还不明白不平等非但影响穷人,还影响在不平等地区周围落户的所有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出发,贫穷迥异于经济不平等。贫穷与一个人拥有和缺少的东西相关,而不平等则描述了金钱是如何分配的,标明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贫穷和不平等却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通过邻里比较感知自己的财富,因为我们潜意识中是通过周围环境感知一切的。无休止的社会比较意味着我们自身的价值从来就不会真正独立于我们周围的有产者和无产者。当富者更富的时候,周围的其他人就会觉得自己更穷了。这种倾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那些豪华古宅和豪车与凋敝的街道相毗邻的高度不平等的地区,会莫名其妙地凸显每个人生活中肮脏不堪的一面。这种“莫名其妙”正是下一章的主题。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不平等如何改变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1] G.M.Fisher,“Mollie Orshansky:Author of the Poverty Thresholds,”AMSTAT News,September 15-18,2008;G.M.Fisher,“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the Poverty Thresholds,”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55(1992):3-14.
[2] L.Saad,“Americans Say Family of Four Needs Nearly$60K to‘Get By,’”Gallup,May 17,2013,www.gallup.com/poll/162587/americans-say-family-four-needs-nearly60k.aspx.
[3] J.Siebens,“Extended Measures of Well-Being: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2011,”U.S.Census Bureau,September 2013,www.cen sus.gov/prod/2013pubs/p70-136.pdf.
[4]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the Wealth ofNations(London:Methuen,1776).
[0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403页。——译者注
[5] B.Wansink,J.E.Painter,and J.North,“Bottomless Bowls:Why Visual Cues of Portion Size May Influence Intake,”Obesity Research 13(2005):93-100.
[6] D.R.Brown,“Stimulus-Similarity and the Anchoring of Subjective Scales,”American Journal ofPsychology 66(1953):199-214.
[7] M.W.Kraus and D.Keltner,“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A Thin-Slicing Approach,”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09):99-106.
[8] T.Mussweiler,K.Rüter,and K.Epstude,“The Man Who Wasn't There:Subliminal Social Comparison Standards Influence Self-Evaluation,”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2004):689-96.
[9] J.Olds and P.Milner,“Positive Reinforcement Produc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Septal Area and Other Regions of Rat Brain,”Journal of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47(1954):419-27.
[10] D.J.Levy and P.W.Glimcher,“The Root of All Value:A Neural Common Currency for Choice,”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2(2012):1027-38;G.Holstege et al.,“Brain Activation During Human Male Ejaculation,”Journal ofNeuroscience 23(2003):9185-93;S.N.Haber and B.Knutson,“The Reward Circuit:Linking Primate Anatomy and Human Imaging,”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5(2010):4-26.
[11] K.Fliessbach et al.,“Neural Responses to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2012):1-9.
[12] A.E.Clark and A.J.Oswald,“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Public Economics 61(1996):359-81.
[13] R.G.Wilkinson and K.E.Pickett,“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A Review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idence,”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2(2006):1768-84.For an accessible overview of this research,see R.Wilkinson and K.Pickett,The Spirit Level: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New York:Bloomsbury,2010).
在肯塔基州的马西奥,60号高速公路沿线附近矗立着13栋A型框架的塔楼,杰森就在这里长大。铁轨横跨公路,载重卡车在此呼啸而过,昼夜不息。在铁轨的另一侧,是一片常年休耕的广阔空地,它被用作隔离铁路和公路的缓冲区,并把楼群与远处的射击场隔离开。人们在这个射击场上用铅弹射击黏土鸽子。由于射击场距离这个小型社区较远,你听不到“发射”的口令声,只能听到枪声。
杰森孩提时代就在烟草厂工作。工人们把宽长的烟叶一张张钉在长木棍上,看上去像热带树叶做成的窗帘。经过一双又一双手,这些钉着烟叶的木棍被传递到烟叶烤房的椽子上悬挂烘干,然后在烤房里蒸上几个月。
椽子的顶端是杰森梦寐以求的工作场所,摔下来的危险极大,但是负重会减轻,因为你无须把烟草举过头顶。这是一份极其艰苦的工作,但是把手染得焦黑的烟草焦油似乎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那感觉就跟尼古丁渗入皮肤一样。
当杰森长成年轻小伙后,他转行在汽修厂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磨掉铁锈,捶打凹痕,用砂纸把油灰打磨进挡泥板和引擎罩上的光滑凹槽中。砂纸让他鼻子里满是尘土,每天工作结束后,他的双手都会流血。但是这份工作比做烤烟草挣得多。在别人的店里干了许多年的小工之后,杰森借了8万美元,开了自己的汽修店,他渴望摆脱小时工身份的局限。结果这家店经营不善,他又深陷债务之中。
因工作需要,杰森一直以来都会购买工业溶剂,所以他购买其他限制性化学品要相对简单一些。像无水氨这样的化学品,能用于肥沃土地,杀死霉菌,也能用来制造冰毒。在多年处理铁锈、粉尘和焦油的工作之后,杰森走上了一条容易得多的道路。他第一次拥有了一辆性能优良的卡车和电脑,也能给家人购买他们以前买不起的衣物和首饰。当他自己开始吸食冰毒的时候,他变得精神饱满,似乎无所不能。一天晚上,在一间无名仓库里,一个装有无水氨的滤毒罐泄漏了,释放出了一种有毒气体,一个邻居打电话报了警,结果杰森在监狱里度过了他的40岁生日。8年后,当他刑满释放时,杰森再也不像他第一天踏进烟草厂大门时那样富有努力工作的热情了。
很多人认为贩卖毒品是快速致富的一种途径。为什么他们会为此铤而走险,不惜吃牢饭以至失去一切,甚至身首异处?社会学家素德·文卡斯特(Sudhir Venkatesh)通过生活在芝加哥内城的“毒品贩卖一条街”的废弃房屋中制毒的贩毒团伙,研究了毒品交易经济学。 [1] 在这几年的研究中,他不仅目睹了毒品交易的过程,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以求发现这种商业模式是如何运行的。
普通的毒贩每小时挣3.5美元,跟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最低工资差不多。许多低级的团伙成员在速食店另有一份工作。在这个团伙的管理链条的上一级,就是成为文卡斯特的亲密线人J.T.那样的“中层领导”。J.T.与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每年能挣3万美元。在芝加哥做毒品交易的人,死亡率高得惊人,大多是争夺势力范围等原因而引起的团伙之间火拼所致。平均每年有7%的团伙成员死亡,这比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时的死亡率还要高出好多倍。
有一天,J.T.和文卡斯特在一家餐厅吃早餐,J.T.出了一道测试题,以是如何思考的:
“假设有两个家伙正在向我(J.T.)供应大批量的半成品。”我(文卡斯特)十分清楚地知道,“半成品”的意思是可卡因粉末,J.T.的团伙可以把它们做成一流的毒品。“其中一个说,如果我(J.T.)可以支付比平常高20%的价格,一年后他会给我(J.T.)10%的折扣,这意味着如果供应短缺,他会优先给我(J.T.)供货。”另外一个家伙则说:“如果我(J.T.)同意一年后以原价向他进货,他现在就会给我(J.T.)10%的折扣。如果是你(文卡斯特),你会怎么做呢?”
“我(文卡斯特)对这个市场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我并不确定应该怎么做。”
“不,你(文卡斯特)不应该这样考虑事情。你总是在游戏中下确定的赌注。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被预测的,供货不能,任何事情都不能。那个告诉你他将从现在开始给你供一年货的人是在撒谎,他还有可能进监狱,还有可能死呢!因此,你应该接受现在的折扣。”
不管是在一个凋敝的农业城镇还是城中的贫民窟,有着像杰森和J.T.一样命运的人比比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比一个来自中产阶级郊区的孩子更有可能进监狱,更有可能辍学,更可能找不到工作。你选择如何对这些个体的故事进行归因,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多人认为杰森和J.T.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对自身的问题负责。还有一些人会注意到贫困或者糟糕的学校教育等因素导致他们缺乏机会。
大多数人曾经都多多少少地思考过这些解释,但甚少有令人信服的观点。一种声音是:这些人纯粹是懒惰,没有责任感或者脑子不灵光。在精英体制下,成功被认为是通过努力工作、责任心和天分才能得到的,而那些在以上方面有性格缺陷的人则更容易犯罪。因为同样的道德堕落会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贫困。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差,是因为懒惰、粗心的父母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的可能性更低,而且智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遗传的。贫困的青少年意外怀孕是因为他们无法无天。那些缺少成功必备品质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利于健康的决定,如吸烟、滥用药物或者暴饮暴食。
关于这个理论的另一个观点是:穷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促进他们拥有诸如努力工作、守信和自力更生等“中产阶级价值观”。无论把这些问题追溯到个人还是文化,论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好的性格会导致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各种问题。
“性格缺陷”理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适用于我们的大脑通常用来寻找原因的惯性回路。当我们尝试搞清一些人的行为的原因时,我们的直觉首先是从这个人身上找原因。这是一条捷径,因为行动经常受信念、意图和能力等因素的引导。当然,性格缺陷理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假设一个人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当然就比那些低智商、自控能力差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我们不考虑“行为同样由特定的情境形塑”这个事实,话题看上去就扯得有点远了。举一个心理学家奈德·琼斯(Ned Jones)领衔的经典实验为例。 [2] 研究参与者聆听了一名学生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他本人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态度,其中半场演讲“支持卡斯特罗”,另半场“反对卡斯特罗”。半数参与者被告知演讲者可以按照他的想法自由选择立场,另一半则被告知这名演讲者为了一个特定立场而呼吁是研究者事先安排好的。在听完演讲之后,参与者被询问:这个“支持卡斯特罗”的演讲者的真实信念是什么。
在演讲者的立场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研究者非常理性地预测,听众会相信演讲能够反映演讲者的真实态度;但是在演讲者的立场被设定的时候,大家就会猜想演讲者对这个主题的评论实际上并非发自内心。但是,这种充分理性化的预测是错误的:无论演讲的主题是自由选择的,还是被事先安排的,听众都猜想这位演讲者讲的是肺腑之言。换句话说,人们似乎不能把预设的立场考虑在内,而是直接把演讲归结为演讲者自身的信仰,甚至是在这个猜想完全不合逻辑的时候。因此,我们在观察一个给定立场的具体细节时,很可能带有强烈的偏见,仿佛它们就是一片玻璃,并基于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解释其行为。这种偏见经常出现,以至于研究者把它称为“基本归因谬误” [3] 。
基本归因谬误适用于许多情形——大学毕业生是聪明的,瘾君子是意志薄弱的,用食品券消费的人是懒惰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分析人比分析情境要容易得多。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们忽略情境的倾向更严重了。当人们在做判断时,手头可能还在干着另外一件分心的事。换句话说,当你在仓促、忙碌、过于放松或是负担过重时,你更有可能无视他人所处的情境。你需要多动一些脑子去考虑,也许这位大学毕业生受益于他的家庭关系,或者那个深陷于低工资工作无法自拔的食品券领取者可能已经在十分卖力地工作了。
对弄巧成拙行为的另一种通常解释与性格缺陷理论不同,它确实考虑了情境问题。该理论声称,是贫困导致了这些生活问题。贫困者更有可能犯罪,因为他们缺乏合法谋生的前提。贫困的学生在学校里表现更差,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没钱聘用顶级教师,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没时间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没有稳定的高薪工作意味着夫妻结婚并组织起稳定家庭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贫困者的饮食往往缺乏营养,也很难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因而存在更多的健康问题。从根本上说,穷人在价值观和行为上与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简单地说,是贫穷的环境导致了贫穷的结果,就像资源缺乏会导致机会缺乏一样。
那些我们从卖弄学问者处听到的陈词滥调,很多是对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的附和,通常包括那些关于贫穷的问题或症状的意涵丰富且富有学术性的尝试性解释。我发现,这些分析具有严重的局限,部分正确,部分错误。性格缺陷与贫困环境论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旧有天性(性格缺陷)与后天培养(环境)之间的较量。与任何关于天性与教育之间的讨论一样,它忽略了更主要的一点:天性和后天培养总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4] 因为作为人类,我们的基因传递的东西,并不是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就像促使果蝇飞向灯光的内在机理那样,而是以特定方式应对环境变化。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理解人类的天性如何让我们做好准备,去应对资源丰富或紧缺的环境,以及高度或低度不平等的环境。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一个在富裕家庭成长起来的人会与一个在贫穷家庭成长起来的人在思考和行为方式上都不同,为什么一个生活在极不平等的环境中的人会与生活在一个较为平等的环境中的人在行为上有差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认识到,不平等是如何改变我们的。
“环境论”背后的思路,其意图是向善的。它避免了谴责与歧视遭受贫困的人,也通过将资源和机会缺乏视为偶然因素而避免了恶性循环。但是“环境论”只是关注这一点,并天真地假设穷人的决定和行为本质上与中产阶级的相同。但就像贫困与富裕都经历过的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人们确实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那些与自己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其中一个差别就是他们思考未来的方式。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到周六我就会去我的朋友斯蒂芬家玩耍。斯蒂芬的家庭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母亲是保险经纪人,父亲是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但是他们的一些行为却让我感到迷惑不解。举例来说,斯蒂芬的母亲会说:“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你们两个有什么计划呢?”毕竟这是周六,她期望我们有一个制订好的出行计划。我们一般会这样回答:“10点到12点打篮球,然后买一个冰镇的墨西哥玉米饼和Sunny D [01] 当午饭,接着打视频游戏到天黑。”看起来就像我们已经全都计划好了一样。当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计划,至少我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吃惊地发现,斯蒂芬正在偷偷地计划我们的日程。对我来说,事先准备看上去都是保守的预科生才会做的事,简直有点娘炮。在我的世界中,男人,就要活在当下。
这种“当下的偏见”与对保守近乎病态的厌恶使我在后来这些年中陷入了无尽的麻烦。当我进入大学和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在接受这种对中产阶级同学来说看上去十分自然的观念和体制的过程中感到十分纠结。在我大学的第三年,我终于放弃了自己的习惯,买了一个每日计划本。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极端的“当下主义”是生来贫困的人的共同经验。
当然,这种生活方式看上去自暴自弃,如果你想要摆脱贫困,就需要对未来做出更好的规划——储蓄或者通过投资创造利滚利的奇迹。但这并不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人思考未来的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在晚间新闻中提供的各种解释大相径庭。为了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成因,我们需要穿越数千英里和数万年去检视,进化是如何让我们做好应对资源稀缺的准备的。
现在请把你自己想象成定居在非洲大草原上的早期人类。你若是一个男人,你将终日打猎或捕鱼。如果你的部落与其他部落陷入冲突,你需要持续监视敌人,因为一场恶战随时有可能打响。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或许正在忙着采集野果和坚果。就像你们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所做的那样。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成年人,你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与其他年轻人打情骂俏,传播绯闻,这不可避免地让绯闻在这个小群体里人尽皆知,因为在这里,大家都彼此熟识。假设存在这些情况,你将会怎样以最佳方式利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呢?
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什么才会让我们最快乐。但是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记住“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快乐。事实上,自然界也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传递了自己的基因。自然界对你的家族是否灭绝,或者人类的种族是否灭绝也没有兴趣。自然界并不支持任何特定的结果,也不支持任何具体的个人或族群。自然界如其所是地发生。而且,自然界也不仅仅是偶然的,一些行为的确导致了有些基因比其他基因被更多地复制并传递到后代身上。因此,这种成功的行为将会在后代中变得更加普遍。这种“创造性毁灭”的节奏在进化过程中创造了精致的模式。因此,为了从进化的角度理解人性,我们需要理解哪种行为会传递更多的基因,在哪些环境中能传递更多的基因。
从进化的立场来说,扩展相关资源的方式只有两种——生存和繁衍。每个有机体在考虑如何分配精力时,都会面临一种权衡(说的是细胞和代谢的能量,而非努力和注意力)。一方面,它可以投入很多能量让自己生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可能为了强壮而生成肌肉,为了保持健康而增强免疫系统;另一方面,它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到生产上,创造出“卵子”和“精子”以及整个荷尔蒙系统和性感的成年人体(使得卵子和精子可以被交换)。当然,我们并不用理性选择控制这种权衡。但是我们体内不同种类的神经系统都在持续不断地规范我们用在不同建设项目上的精力(本章要讲的压力与健康会提供更多细节)。
生存和繁衍,这两种方式哪种能为传递人类的基因提供最好的机会?这可不一定。此外,它还依赖于时代的好坏。在繁荣的时代,未来看上去是安全稳定的,这就是你有可能健康长寿的标志。如果你等到自己真正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之后才生孩子,你将会留下更多的子嗣。你需要贡献自己的一切付出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使他们能够繁衍生息,也许你还能帮忙带孙子辈呢。
在艰辛的时代,未来是不确定的,敌人潜伏在每一片草丛之后,繁衍的可能性就变小了。你也许还没活到生小孩就死了。在这些情况下,早生、多生才是有效的。如果你最终决定繁衍,最好尽早生孩子。第一种方式是进化生物学家称为投资未来的“慢战略”;第二种方式则是“快战略”,说的就是“快速生活,早早死去”。
当然,早期智人并没有有意识地采取策略使自己的基因适配率达到最大化。然而,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那些在日子难过的时候采取快战略,在日子好过的时候采取慢战略的人,比那些对环境反应不太敏感的人留下了更多的子嗣。结果是,在下一代有很多人倾向于在艰苦时光的快战略和舒适时光的慢战略之间切换。如今,经过了无数世代的传递,我们成了那些十分擅长采取这些战略的祖先的后代。
动物通过在连续不断的快与慢中转换,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这一点生物学家在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譬如,他们观察到,同样种类的蝴蝶,若生活在有许多天敌的地区会繁殖得更早,用更少的代谢能生长,用更多的代谢能繁殖;若生活在天敌较少地区,则会活得更久一些,因此也会采取相反的途径——繁殖得更晚。然而,确凿证据是在科学家开始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之后才获得的,这些证据表明,的确是危险的环境决定了适应性的不同。
在一项研究中,生物学家用10只“亚当”果蝇和10只“夏娃”果蝇繁殖出了800只果蝇。 [5] 然后,他们把这些果蝇分成两组基因相同的群体。一个组幸运地被分配到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群体中,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和繁殖,可以做任何果蝇喜欢的活动。另一组果蝇就没那么幸运了,每周有两次,90%的“早死”果蝇组会被新的果蝇杀死并补位。研究者将这个过程持续了四年。
阅读关于这项实验的科学报告会让人紧张不安。你不由得从果蝇的视角来想象这种境况,发现自己陷入了科幻小说式的梦魇之中:一群可怕的、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巨人,让你认识的所有人一个个地消失。这个实验情景被委婉地描述为“高成年死亡率处理”,死亡率能够被精确地计算出来:“一个成年个体存活一周的可能性=0.01”。
除了暴力之外,这项研究也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早死组”的果蝇繁殖得更早,“早死组”的雌性果蝇也比“安全组”的雌性果蝇排出更多的卵子。这只是“快生早死”理论预测的结果。果蝇并不是通过环顾四周观察判断出自己即将陷入危险,然后才决定尽快配对的。这种能早点繁殖的果蝇只是为了在下一代中留下更多的子嗣。
1991年,心理学家杰伊·贝尔斯基(Jay Belsky)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观点, [6] 基于对进化快慢的权衡,在充满压力或无秩序的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女性早生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当时相关的数据还不是很多,但已经足够验证杰伊的理论。几年后,心理学家马戈·威尔森(Margo Wilson)和马丁·戴利(Martin Daly)开始挑战对芝加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芝加哥是一个社区城市,你可以从林肯公园的林荫大道、破铁皮路灯和红砖建筑开始研究。如果你旅行到南部的恩格尔伍德,就可以从它光秃的水泥路、无窗的建筑和散落着碎玻璃的人行道开始。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短短12英里中就跨越了一些隐形的边界,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在某些方面,你确实已经跨越了边界。
威尔森和戴利观察了芝加哥所有社区中的女性生第一个孩子时的平均年龄。 [7] 果不其然,贫困地区的女性生孩子更早。接下来,他们把每个社区中女性生头胎的年龄与这个社区的平均寿命相联系,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预期寿命是促成更早繁殖的最大压力源。这种相关性是很强的,几乎达到一比一:在预期寿命降低的时候,女性生育的年龄也会降低。就像“快生早死”理论预测的那样,当人们死得早时,他们就会更早地生孩子。
自从这项开创性的调查开启后,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威尔森和戴利的实验结果。在贫困或危险的环境中长大的女性生孩子更早。她们生孩子的平均数量也更多,这也是增加基因传递机会的另一种方法。
因此,贝尔斯基提出的理论看上去被数据证实了。但是贝尔斯基并不仅仅预测了早生孩子这件事,他其实走得更远。他认为在逆境中长大的女性之所以生孩子更早也更频繁,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对她所处环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程度的回应,这很有可能在心理和生理上影响她们与周围世界以及其他个体相处的方式。贝尔斯基预测,在贫穷、危险、无秩序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月经的时间和进入青春期的时间都要早于在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女孩。如果是这样,她们生孩子的平均年龄就更早,因为她们成熟得也更早。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这说明家庭环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也在生理上对他们产生影响。
这项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阵小热潮,很多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开始持续跟踪某些家庭,从这些家庭的新生儿开始,直到他们的孩子出生。如果的确是无序的环境导致了出生率变化,那么即便你只了解女孩所在的社区或者家庭状况,而对她们本身一无所知,也能在女孩出生之前就预测出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经过一个又一个实验,贝尔斯基的预测被证实了。到21世纪中叶,在贫穷无序的艰苦家庭里长大的女孩比那些在更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要更早进入青春期。 [8]
这些结果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推进了贝尔斯基的理论。对动物的研究集中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但对人类的研究则比研究动物要复杂得多,其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出生率和死亡率。更早进入青春期和更早生育不仅和预期寿命有关,也和贫穷、家庭中的父亲缺位以及该地区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有关。即使这些困难本身不是致命的(至少不是直接的),它们看上去也预示着和高死亡率同样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在人类中间,对快和慢的权衡产生的后果到底有多广泛呢?心理实验表明,这种后果比任何人的事先预测都更加普遍,它以与繁殖毫不相关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决定。它们之中关于现在与未来最重要的权衡往往是和金钱有关的。财务咨询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省下每天喝拿铁咖啡的3美元,每年就会增加1000多美元的存款。但是这意味着每天你都要面临一个选择:我到底是想在年底的时候银行账户上多出这1000美元,还是抓住当下的美好——现在就喝上一杯拿铁?
同样的权衡也隐藏在更大的生活决定背后。我是风物长宜放眼量,把时间和金钱投资到上大学然后拿高薪,还是现在就找份工作保证基本收入?我是做一份规矩的工作,循规蹈矩地生活,即便我可能一辈子都在为财务挣扎,还是干脆就去贩毒?如果我选择贩毒,也许就会长远地失去一切,以破产告终,进监狱或者死亡,但是也许现在就会挣很多钱。
即使对富裕和贫穷的短期感觉也会让人们或多或少地变得短视。回想一下前几章那些对贫穷和富裕的主观感觉拥有的强大效应,这种效应通常基于我们如何把自己与他人进行衡量。心理学家米奇·卡伦(Mitch Callan)和他的同事把这两项原则融合到了一起并预测,当人们感到自己穷困时,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会用尽一切手段迅速获取,对未来则视而不见。 [9] 当让人们感到自己富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从长计议。
他们的实验首先探究式地提问实验参与者的财务状况、消费习惯,甚至他们的个性特征和个人品位。他们告诉参与者,实验需要所有的细节信息,因为电脑程序将计算出个性化的“相对可支配收入指数”。参与者被告知,电脑会给他们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显示了他们和年龄、教育水平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相似的年轻人在金钱数量上的比较结果。事实上,电脑程序并没有做这样的比较,而只是展示了一个闪烁的进度条和一串文字:“计算中,请等待……”然后,电脑给参与者提供了随机报告,告诉其中一半人,他们比跟他们差不多的大多数人更有钱,而另一半则被告知他们手里的钱比跟他们差不多的大多数人要少。
接下来,参与者被要求做一些财务决策,有一系列方式可供选择:更小却更快的收益,或更大也更慢的收益。举个例子,他们也许会被问及:“你愿意今天拿到100美元,还是下周拿到120美元?”“你愿意今天拿到100美元,还是下周拿到150美元?”在他们回答了许多这类问题后,研究者就能计算出参与者会把多少钱放在即刻的收益上,多少钱会让他们愿意等待一个更好的长期回报。
这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觉得贫穷时,他们在关于快慢的权衡中就倾向于速战速决,希望得到即时回报。但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相对富裕时,就会做更加长远的考量。为了强调这一点——这并不单纯是在真实世界中没有影响的抽象决定,实验者对第二组参与者再次做了这项研究。这一次,实验者没有使用假设性的选择,而是给每个参与者发了20美元,并给他们提供了一次用这20美元参与赌博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把这些钱装进腰包,然后退出回家,也可以选择与电脑玩一把扑克碰碰运气,也许会赔得精光,也有可能挣更多的钱。当参与者被弄得感觉自己是相对富裕的时候,60%的人会选择赌博。当参与者感到自己相对贫困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飙升至88%。感觉贫困会让人们更愿意孤注一掷。
这些试验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并不需要整个童年都处于贫困或富裕环境中,才能改变人们短视的程度。即便只是一种没有其他人富裕的主观感觉,就足以启动“快生早死”的生命路径。
素德·文卡斯特追踪的大多数贩毒团伙成员,都挣着同样微薄的收入,并与他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并不能靠贩毒变得富有,而工作又如此危险,为什么还要选择干这行呢?原因是,还是有少数处于团伙顶端的成员,一年可以挣几十万美元。他们的财富令人侧目——开豪车,穿华服,佩戴珠宝四处招摇,到哪里都前呼后拥。团伙中的普通成员并不会关注彼此的生活,因此推断不出这是糟糕的营生。相反,他们关注的是那些处于团伙顶端的成员,想象着自己能成为他们那样。尽管成功的概率极低,却甘冒骇人的风险。
“快生早死”理论解释了当人们处于贫穷状态时,为什么更关注此时此地,而忽略未来。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第二章描述的研究表明: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比例更高,这种情况甚至存在于中产阶级成员之间。在过去的30年间,不平等现象激增的一个最令人困惑的方面是:几乎所有的财富变化都发生在最富有的人群中间。一旦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就与1980年没什么差别。而位于最顶端的1%人群的收入及财富则飙升,同时,即便他们的财富飙升了,那些位于前0.1%的人则会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那么,超级富人的收入是如何对其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呢?
从大黄蜂的蜂巢中,我们能找到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生态学家拉夫·卡他(Ralph Catar)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外的小岛上研究野生大黄蜂的摄食习惯。 [10] 大黄蜂主要从两种花上采集花蜜,一种是海红(seablush),另一种是矮越橘果。海红是一种顶端有着粉色大花瓣的高茎花。一片海红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绿色夏天背景上成千的粉色点彩。矮越橘果是一种有着野生灌木外表的低矮植物,有的会结几个蓝色的浆果,悬着几朵铃铛似的白色小花,如果你看到成片的矮越橘果,很有可能误认为是一片野草。
卡他注意到,在大黄蜂看来,海红和矮越橘果这两种花是完全不同的。平均而言,昆虫可以从这两种花中获得的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选择海红是有保障的。如果大黄蜂在一片海红中觅食,它们绝不会饿着离开。因为每朵花中含有的花蜜量都差不多,不多也不少,这同样意味着它们也绝不会吃到太多花蜜。因此,海红是一种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恰恰相反,矮越橘果是一种大黄蜂玩的“21点”游戏:一些花朵中的花蜜多得像中了头奖,另一些却一无所有。吃矮越橘果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
卡他开始检验一套关于风险承担的进化理论,我称之为“没有什么可失去”理论。该理论认为,从大黄蜂到狩猎采集者,任何觅食生物承受风险的量级取决于它的需求程度。一只吃饱了的大黄蜂,可以选择海红以保证不饿死。但设想一下,一只快要饿死的大黄蜂若只依靠海红中贫乏的花蜜,很可能无法存活。那只濒临饿死的绝望大黄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它会抓住这个机会,匆匆找寻矮越橘果中的意外之喜。也就是说,随着需求增大,风险也会加大。为了检验这个理论,卡他必须比较大黄蜂在吃饱和饥饿两种状态下的觅食选择。他和助理们每天要走访14个大黄蜂聚集地,在实验的前几天,他们会从一些特定的蜂巢中用小管子偷偷吸出花蜜,然后转移到其他的巢穴中。后来的几天,他们会把程序颠倒过来——此前被偷走蜂蜜的蜂巢现在会被给予额外的花蜜。研究人员随后会统计每天每个聚集地中有多少大黄蜂去各个花丛,为了识别它们的归属地,大黄蜂会被标记成不同的颜色。正如卡他所料,当大黄蜂收到额外的花蜜时,它们会选择安全,在海红花丛中觅食;但是当它们的花蜜被转移时,它们会直奔矮越橘果花丛而去。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计算出最佳选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对人类来说也是一桩难事。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理性选择意味着收益最大化,可以通过将“回报的大小”乘以“得到它的可能性”计算出你的“期望效用”。因此,一个有90%的机会赢得500美元的选择,其期望效用高于有40%机会赢得1000美元的选择(500×0.9=450美元相对于1000×0.4=400美元)。但是大黄蜂的例子表明,选择的种类并不一定与期望效用的模型完美吻合。同样,这个例子也证明,很多其他物种在做出冒险选择时,与大黄蜂在窘迫之际冒大风险显示了同样的倾向。
人类便是那些物种之一。设想一下,如果你欠了1000美元租金,今天到期,还不上就会无家可归,你会怎么做?若你此刻身处一场赌局之中,你会选择有90%的概率赢500美元,还是有40%的概率赢1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以小概率赢1000美元——因为一旦赢了,他们的需求就能满足。尽管从“期望效用”角度来看,这是非理性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讲,这又是理性的。因为有时满足基本需求,比数学上所谓的“最优交易”更加重要。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的相同模式表明:基于需求做出的选择,对于进化来说也是适用的。无论是拥有微小大脑的大黄蜂,还是试图满足需求的人类,我们并不总是寻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米克·贾格尔逻辑”(Mick Jagger logic)。如果我们不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就可以试着得到我们需要的。有时,这意味着要冒巨大的风险。
在第二章中我们发现,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判断自己需要什么,与顶层的人比较,比同底层人比较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如果不平等的加剧会让人觉得自己需要更多、更高层的需求,从而导致冒险选择,它就揭示出了不平等与风险之间新的根本关系:无论你是贫农还是中产,不平等本身就可能导致人们趋向风险高的行为。
为了检验不平等是否真的提高了冒险选择的概率,我和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11] 研究的参与者被要求做出一系列赌博式的选择,包括低风险回报的选择(例如有100%概率赢得15美分)和高风险回报的选择(例如有10%的概率赢得1.5美元)。他们被分为两组,在开赌之前,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此前参与者做法的有关信息,并以此作为关键的实验因子。在“平等”组里,参与者被告知,表现最好的人比表现最差的人可多挣几美分;而在“不平等”的组里,参与者被告知,表现好的人比表现差的人挣得多得多,表现差的人几乎一无所获。两组实验情境的平均所得是相同的。在参与者被告知前人的做法之后,他们表示了在游戏中需要多少钱才满意,随后他们自己来玩这个游戏。
正如我们所料,相比“平等”组而言,“不平等”组中的参与者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才能满足。在不平等程度很大的情况下,参与者感到需求强烈。结果就是:当“不平等”组做出赌博选择时,他们会选择更高的风险,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实验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两组人有着相同的平均收入和教育程度,初始时有着相同数量的钱,他们也都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因此不必担心之前赢的会输掉。在知道玩得好与玩得差之间会有巨大收入鸿沟时,“不平等”组选择了更高的风险。这个实验为不平等本身会引发风险行为提供了第一证据。
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在“不平等”组里,一小部分玩家赢得了大额奖励,但大多数人一无所获;在“平等”组里,没有人得到极高的回报,同样,也没有人一无所获。换句话说,通过发起风险更高的选择,不平等导致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更大的差别。实际上,不平等孕育着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就是一个培养皿,他们可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并随机分配,这对于弄清因果关系非常必要。将问题带入实验室的过程中,他们将问题从常规情况中剔除。对我们的实验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弄清,在自然环境中是否也会发生相同的动态过程。就普通人更加无序的生活而言,不平等是不是他们风险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研究人员衡量风险选择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参与者的行为。但是谈到许多让人们陷入麻烦的风险时,这种方法就存在问题——“女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调查,请问在过去的一年中,您做过几次愚蠢的财务选择?您做过几次对健康有风险的行为?譬如没做安全措施的性生活。您酒驾过吗?您有几次无视法律,涉嫌使用和贩卖毒品?”这些显然都是伦理问题,而且需要让人们承认自己做过的一些极尴尬且非法的行为。即便你提出了这些问题,也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因此,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来衡量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行为。我们转而使用谷歌,寻找当人们涉足特定种类的风险行为时可能搜索的术语,通过识别可能引发真正问题的三个领域的风险决策开始我们的研究,它们分别是财务决策、性行为及酒精和毒品的使用。一旦我们开始关注性、毒品和钱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如果我陷入了这种类型的风险行为,我会搜索什么?
举例来说,人们在谷歌上搜索“彩票”“发薪日贷款” [02] 这样的词条时,很可能是已经陷入开销风险了。在性风险的衡量上,我们把搜索“紧急避孕药”和“性病测试”这样的词条计算在内。衡量毒品和酒精的相关风险时,我们关注的搜索词条是“如何避免宿醉”和“如何通过毒品检测”。当然,一个人在搜索这些词条时,也许并非与涉及这些危险行为有关。但通常,如果有更多的人涉及性、毒品和财务风险,那么你就会发现这类搜索更多了。
有了在谷歌上得到的数十亿个此类数据点,我们想知道:人们搜索这类词条越多的州,是否就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州。为了减少单个搜索词条本身特性的影响,我们将六个词条合到一起计算出综合风险承受系数。接着,我们描绘出该系数与各州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正如谷歌搜索估计的那样,越不平等的州,风险承受系数越高,在对每个州的平均收入进行统计学调整后,两者依然保持着强相关。
如果用谷歌风险承受系数追踪现实生活中的风险行为,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它与贫苦生活相关联的结果。 [12] 因此,我们选择谷歌系数并检验其能否解释第二章中提及的不平等和关于10个主要健康与社会问题的理查德·威金森和凯特·皮凯特系数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确,谷歌风险承受系数与生活问题系数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通过缜密的统计学分析,我们发现,不平等是风险选择的有力预示,而风险选择又预示着健康和社会问题。这些发现表明,有风险的行为是帮助解释不平等与日常生活中的坏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的一条途径。当我们同时考虑这种相关性与实验室实验提供的因果证明时,证据就会变得更加有力。
本章描述的实验对于理解不平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实验才能从个体的个性特质差异中区分出环境效应。诚然,在每个实验组中,都会有一些杰出人士和愚蠢的人,有天生自控力就强的高尚灵魂,也有不负责任的混混。由于这些人是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中的,所以想要使各组间的人在性格和能力上的差异程度保持一致是完全不可能的。换言之,我们看到的这种差异,正是由实验因子造成的。在这个例子中,决定的做出取决于不平等的高低。
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Bradford)是16世纪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他在国王爱德华六世(King Edward VI)治下声名鹊起。然而,在爱德华六世死后,玛丽·都铎(Mary Tudor)王后继位,他的命运迅速转变。作为天主教徒,数以百计反对她的人,都被玛丽王后处死在火刑柱上,她因此被称为“血腥玛丽”。在被囚禁于伦敦塔期间,布拉德福德看到其他囚犯被领到大厅执行死刑,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不知道自己是会被释放还是处决。他和他的狱友谈到,改变他命运的东西,并不在他的掌控中,它无法预测,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能改变的。实验就是温柔的提示者,用约翰·布拉德福德的话来说,就是“上帝的恩典指引着我” [13] 。如果我们深入地理解行为实验,就会变得谦卑。它们挑战着我们自身的成败尽在自己掌握中的假设,就像约翰·布拉德福德那样,我们并不是自己的思想、计划和一己之力的简单产物。
这些实验表明,任何一个普通人,当身处不同的情形之中时,表现也会不同。设想一下,你是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研究计划,而且没有伦理审查委员会限制你的行为,你决定将一万名新生儿随机分配到不同地方的家庭中培养——一些孩子分配到亚特兰大城郊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手中,另一些分配到密尔沃基城里的单亲妈妈手中,诸如此类。我们看到的研究表明,你给他们分配的环境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主要的影响——被分配到得克萨斯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州的孩子,比那些分配到艾奥瓦这种更平等州的孩子,结局更差,尽管得克萨斯州同艾奥瓦州的平均收入几乎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在不平等的地方,不好的事情更容易发生在人们身上。而且,在不平等的地方成长的孩子,其表现也会呈现某种程度的差异。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尽管被你随机分配的孩子在生命之初具备同样的潜能与价值。
不公平性与风险选择的实验结果让我再次想到了杰森。他不仅是我的另一个研究对象,还是我的兄长。我也曾从事烟草工作,感受过烟草焦油滴在皮肤上吱吱啦啦的声音。我在兄长的汽修店工作,在炎热的夏日打磨底漆,我的指纹都脱水消失了。当我进入高中的那个夏天,杰森还在经营着汽修店。他把车停在我父母家门口,问我是否愿意去法兰克福兜风,他正在售卖一辆低价买进并修理过的汽车,因此需要去州府变更原始所有权。他既想把我这个无聊的宅男从屋子里揪出来,又想在单程两个半小时的驾车旅途有个伴儿。在他的卡车进入公路减速后,我们谈论了一些严肃话题,这是我们以往不曾谈论过的,我隐约感到他有心事。
我们前方的车行十分缓慢,最终停滞下来。杰森盯着前面一串红色的刹车灯,忽然向左打轮驶出公路,驶入长满青草的中间带,这里比两侧的沥青路面宽好几倍。我们回到上坡,然后开到对面的车道上,沿着它快速行驶,在下一个出口驶出公路,为躲避拥堵而上了一条乡间小路。“要我在那里等才见鬼了呢!”杰森解释道。过了一会儿,我们又驶回公路,杰森拿出一个小的雕花木盒,从这个神秘小物件的一侧抽出一个小不锈钢管,又从另一侧推了进去,拿出一小堆碎大麻叶,塞到其中一端。他用膝盖控制方向盘,用打火机点着了管子的一端,原来这是一个烟斗。我被这个有着天才设计的小物件深深吸引,我认为用它抽烟比在开车时卷烟卷还需要练习更多次。
在公路上继续安静开车的杰森,在谈到他无法预知自己的汽修店今年还能否存续时说:“我绝不会一无所有,所以我得去做我现在就想要做的事。”
[1] S.A.Venkatesh,Gang Leaderfor a Day: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New York:Penguin,2008).
[2] E.E.Jones,“How Do People Perceive the Causes of Behavior?,”American Scientist 64(1976):300-305.
[3] L.Ross,“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1977):173-220.
[4] R.Sapolsky,“A Gene for Nothing,”Discover18(1997):40-46.
[01] Sunny D,美国一种流行的儿童橙汁,水果零食。——译者注
[5] S.C.Stearns,M.Ackermann,M.Doebeli,and M.Kaiser,“Experimental Evolution of Aging,Growth,and Reproduction in Fruitflies,”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97(2000):3309-13.
[6] J.Belsky,L.Steinberg,and P.Draper,“Childhood Experience,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and Reproductive Strategy: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ization,”Child Development 62(1991):647-70.
[7] M.Wilson and M.Daly,“Life Expectancy,Economic Inequality,Homicide,and Reproductive Timing in Chicago Neighbourhood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1997):1271-74.
[8] M.Del Giudice,S.W.Gangestad,and H.S.Kaplan,“Life Histor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in The Handbook ofEvolutionary Psychology,D.M.Buss(ed.) (Hoboken,NJ:John Wiley and Sons,2015).
[9] M.J.Callan,N.W.Shead,and J.M.Olson,“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Delay Discounting,and Gambl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011):955-73.
[10] R.V.Cartar,“A Test of Risk-Sensitive Foraging in Wild Bumble Bees,”Ecology 72(1991):888-95.
[11] B.K.Payne,J.L.Brown-Iannuzzi,and J.W.Hannay,“Inequality Increases Risk Taking,”Working Paper,2016.
[02] 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一种无须抵押的小额短期贷款,以个人信用做担保,其依赖的信用依据是借款人的工作及薪资记录,借款人承诺在下一发薪日偿还贷款并支付一定的利息及费用。这种贷款自20世纪90年代在北美大规模兴起,对申请人的资信要求更低,批评者认为这将怂恿他们消费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些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借款人承认,他们在一年内使用发薪日贷款6次以上,这部分借款人多为陷入债务循环的低收入者,无法偿还本金。——译者整理自维基百科
[12] B.K.Payne,J.L.Brown-Iannuzzi,and J.W.Hannay,“Income Inequality,Risk Taking,and Social Outcomes,”Working Paper,2016.
[13] E.Bickersteth,A Treatise on Prayer:Designed to Assist in Its Devout Discharge:With a Few Forms ofPrayer(n.p.:A.Van Santvoord&M.Cole,1822).
格伦维尔男爵 [01] 此时正在凡尔赛宫,像往常一样,环绕着他的依然是各种珍宝和奢侈品,这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1] 然而,也正是此刻,他却发现自己与混乱是如此接近,他感到有些迷失方向了。1791年,法国传统的三级会议被一个又一个新的议会形式取代,每一种形式都在碎片化为派系纷争后迅速崩溃,然后变成下一种形式。国王路易十六挣扎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在说服与强迫的声音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真正摇摆不定的是他的项上人头。
正当最新型的议会第一次聚会时,议员们在混乱之中把自己划分为志趣相投的团体。格伦维尔男爵声称:“我们开始认识彼此——那些效忠于宗教和国王的人占据了国王椅子右边的位置,以图避开对手阵营的喊叫、咒骂和无礼。”希望废除君主制的激进革命者和致力于启蒙的理性精神而非教堂权威的人则同时倒向了左翼,而那些观点更加温和的人占领了大厅中央。
即便事先没有计划,座位的安排也是有迹可循的。在老三级会议上,国王曾邀请神职人员(第一级)和贵族(第二级)坐在自己的右手边;劳动人民(第三级)则坐在他的左手边。像全世界许多文化习俗一样,“犹太—基督教”传统更希望自己的党派被允许在右边就座。因为在《圣经》中,耶稣就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在法语中,“笨拙”(gauche)一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左边”;但在英语中,我们用这个单词表达“不优雅”或“不懂人情世故”的含义,跟格伦维尔男爵鄙夷的那种“喊叫、咒骂和无礼”的意思差不多。类似地,法语中的“向右转”(à droite)在英文中变成了“圆滑的”(adroit),意为“有技巧的”或“有天分的”。根据格伦维尔男爵对法国大革命相关事件的描述,那时国王已不再告诉贵族应该坐在哪里,但看上去他的支持者坐在右边会让他更舒服些,他的敌对者则坐在左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作家对这次会议的报道开始把不同派系缩写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右”和“左”因此进入了政治学词典,分别对应“保守”和“自由”的描述。假使凡尔赛会议厅的陈设不是如此排列的,我们今天也许会把保守派称为“前”,而把自由派称为“后”。
除了“右”和“左”的历史渊源之外,这个标签也保持了它的一些原始含义。在政治上,“右”就是好的,“左”就是不好的吗?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好”是对谁而言的。从国王的角度来讲,“右”在想要保持君主制和按老方法做事情的传统主义者看来是好的,而在那些想要改变社会规则的人眼中则是坏的。这种所谓的“好”和“坏”的确存在,但仅仅是出于那些在传统权力结构中掌握着权力的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今天与18世纪的法国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议题会与自由或保守的视角并列在一起呢?原因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支持妇女有权利堕胎的人同样希望增加高收入人群赋税?为什么坚持持枪权的人同时也不信任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发现?为什么人们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与他们在同性恋婚姻上的观点也有联系呢?
政治心理学家这些年来曾提出过许多框架,试图解释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核心路径上的不同。它们是严格教育与宽容教育相对抗的产物,还是僵化思维与灵活思维的对抗?抑或宗教世界观与世俗世界观的对抗?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 Jost)回顾了历史学理论和很多经验主义的研究,发现左派和右派在两个基本方面始终与彼此不同。 [2]
其中最首要也最明显的区别是:保守派大多希望保持传统和维持现状,而自由派则希望看到社会的变化。然而,从两派各自的立场上看,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保守派不单纯是为了让事物保持原样而要求维持现状。与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一样,他们倾向于认为,一个陷入混乱的社会可能是最坏的。因此,保守派对社会秩序受到的威胁(叛军)或者来自内部的威胁(潜在的革命)十分敏感。由于公民秩序很难获得,所以保守派坚信我们应该努力维护它。这通常表示他们会选择相信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方法。即便这意味着放弃一些通过改变社会规则来改善社会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
同样,自由派也不单纯是为了要改变而希望变革。他们倾向于把社会的一些方面看作是运转良好的,而把其他方面看作是运转不良的。既定的做事方法导致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因此,自由派并不深受传统影响,还认为自己迫切需要去改变他们认为失效的事物。比起保守派,自由派在运用人类理智力量发现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上更有自信。简妮·杰奎斯、卢梭和约翰·洛克等哲学家的足迹,激励着自由派继续重写社会规则,以期能持续地改善社会。
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第二个根本区别体现在他们接受不平等的意愿上。同样,大部分保守派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愿看到不平等发生。相反,他们把不平等看作是强调个人权利、能力和责任的结果。当人们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胜出时,结果总是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与许多自由派的看法相反,大部分保守派不会因为等级制的理念本身而备受鼓舞。他们只是不会像自由派那样受到困扰而已。
自由派与许多保守派的视角不同,他们对个人权利与责任,对市场竞争的理念并没有敌意。相反,他们把个人价值看作竞争性市场中决定胜败的唯一因素。他们倾向于把经济体系当成一个整体,而不只是着眼于其中的个人玩家。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把以下因素考虑在内:垄断、校友关系、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塑造个人成就的优势和劣势的循环等。因为这些都与个人价值无关。他们对于“大政府”没有特别的喜好,并常为保守派对政府规模的痴迷感到困惑。自由派把政策和市场都看作改善社会的工具,有效但不完美。毕竟,生活太复杂了,复杂到难以从某个单一的角度去估量。就像自由派总是喜欢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数据和经验中得知,大部分生来一无所有的人会以贫困终其余生,而大部分生来富有的人则始终富有。尽管如此,正如保守派的惯有论调,个人天分和责任感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使得一些杰出的个人能够跨越贫穷和有限的机会,赢得巨大的成功。事实上,这个整体系统无须适用于这个系统中的所有个体。
想象一下嗡嗡低鸣的椋鸟群,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中,每一只鸟都在根据自己的喜好飞行。待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只鸟都会受到保护,这使它们免于老鹰和其他捕食者的侵略。鸟儿们并不知道这个群体接下来要飞向哪里,也没有头鸟来确定整个鸟群的航向。 [3] 鸟儿们仅仅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获得周围鸟儿活动的信息,并努力与它们保持接近。当一万只椋鸟都跟随着同样简单的规则运动时,结果就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阴影掠过地表——一会儿呈波浪状,一会儿呈旋涡状,突然又变成螺旋状,分解成猛犸变形虫然后又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就像诗人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形容的那样,“这是什么东西?它们像一个醉汉在天空中乱涂的指痕!”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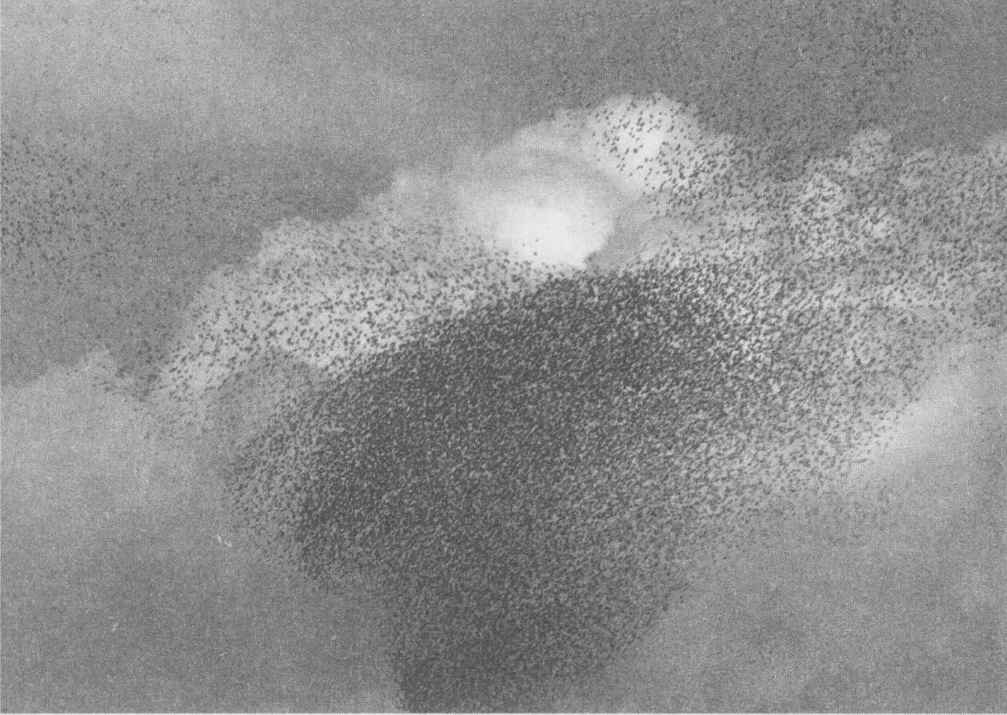
图4.1 椋鸟的低语
资料来源:David Buimovitch/AFP/Getty Images。
当你把这个鸟群当作一个整体去考量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机体,想要掌握这个机体之中的个体行踪是很难的。而且,当你关注单只椋鸟的运动时就会发现,它的行动并不与鸟群整体的运动方式相同。在任何时刻,某只椋鸟可能向前运动,而整个鸟群都是在向左运动;在一队椋鸟盘旋的时候,其中一只椋鸟很可能忽然俯冲向下。这个整体就像一场视觉幻影——一会儿呈现鸭子的形状,一会儿又变成一只兔子,你不可能同时看见个体和整体的样子。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和经济:你可以关注个体,也可以关注系统,但是你很难同时关注两者。保守派关注系统内的个体,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责任找一份工作,那个年轻女人应该避免让自己成为一名单亲妈妈。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应该承担后果。自由派关注系统,他们发现在贫穷成为常态的地区,贫穷就会代代相传。即使孩子们十分努力,也很少有人能逃出贫穷的命运。如果你想要预测谁会找到工作,或者谁会变成单亲妈妈,你可以从评估他们父母的收入和他们所在学校的口碑开始。
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两种视角都过分简单化,因为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个体责任感、才能和努力工作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也都承认环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两派的侧重点不同。当整个系统被放在聚光灯下时,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作用就会被凸显。而当聚光灯对准个体时,等级制和不平等就可能落到你看不见的黑暗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对抗,等级制与平等之间的对抗,这是引导道德罗盘的两项基本原则。然而,并没有一种哲学推理能够说明:为什么那些支持传统的人也必须接受等级制,或者为何支持变革的人同样应该渴望平等。约斯特和他的同事指出,使以上概念并列在一起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多西方社会的等级化程度就降低了。君主制让位于民主制,奴隶制被废除,女人和黑人获得了投票权,他们至少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平等。在21世纪,我们目睹了平等权甚至扩展到了同性恋和变性人等群体。基于这些历史趋势,旧的权力结构更倾向于等级化,同时新的权力结构则更倾向于平等。对传统的偏爱自然更可能伴随对不平等的容忍,而对变革的青睐则意味着拥抱更大程度的平等。
历史上曾发生过有趣的意外,说明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偏爱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结并非铁板一块。 [5] 心理学家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的信仰。共产党政府几十年的极权统治推进了相对的经济平等,而苏联的解体又导致了不平等的戏剧性扩大。那是一段混乱的时光,基本没有规则来管控资本市场。普通人丧失了经济安全,而一小撮关系硬的人却成了百万富翁。麦克法兰和他的同事测算了人们对新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旧共产主义时代的支持情况。他们也评估了俄罗斯人对传统权力和打破稳定的偏好。与北美和西欧不同的是,在俄罗斯,对传统的崇敬与对更大程度的平等的渴望是紧密相关的。对旧政体的渴望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这取决于政体的本质。
我们已经分类讨论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但通过人们的政治立场给人分类是非常刻板的,比这些人本身还要刻板和极端。我们所有人都会时不时地发现自己正在沿着“对方”的路线思考,事实上,我们在政治上都具有多面性。
在大部分工作日,我都会沿着教堂山的主要街道——富兰克林街散步。每当我走在这条街上,准备吃午餐或喝咖啡的时候,都会遇到乞丐跟我要钱。我为自己的“友好姿态”感到惊讶:有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些钱;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走开了。但是,比起我不那么稳定的行为,更让我困扰的是我飘忽的思绪。有些时候,当我听到“有零钱吗?”这句话时,我眼前会浮现一个正在经历一段难熬时光的人的形象:譬如一些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起步的倒霉透顶的人,还有在最落魄的日子里需要一点帮助的人。在其他时间里,我也遇到了一些十分不负责任的人,他们甚至一直赖在床上。还有一些人,如果把他们缠着其他人要钱的劲儿放在早起工作上,他们早就被高薪聘用了。我经常在一小时之内就会产生以上所有不同的想法。为什么我们的意识流有时看起来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之间不断切换呢?
心理学家阿伦·凯(Aaron Kay)和理查德·艾巴赫(Richard Eibach)声称,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携带着“意识形态的工具箱” [6] ,我们把自己的政治信仰当作一系列稳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逻辑和事实的支撑。然而事实上,它们更像是一些工具的混合。我们依据某个特定时间的需要做出选择。有些时候,我们选择的意识形态原则取决于我们最近的想法。如果我在沿着富兰克林街散步之前的几分钟阅读了一条关于无家可归的人犯罪的新闻,我就会以更负面的方式想象下一个我遇到的乞丐,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观念刚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可达性”。大脑就像谷歌一样,保存着最近刚刚使用过的处于意识前沿的想法,因此,我们即刻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它们。可达性并不依循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如果我向你展示“海洋”和“月亮”两个词, [7] 接着就要你给一种优质洗涤剂命名,你很有可能说出“潮汐”二字,洗涤剂同海洋和月亮之间并没有逻辑相关性。如果你近期使用了内在关联的意识网络,你将来更有可能在这个网络中遨游。
我们内心能在自由和保守之间切换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并不按照我们认定的方式去追踪我们思维上的逻辑一致性。心理学家拉斯·霍尔(Lars Hall)、佩特·乔纳森(Petter Johansson)和同事在一项令人惊叹的研究中,展示了人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易变,他们把这项实验称为“选择盲目” [8] 。他们对瑞典的选民就一系列国家选战中的争议话题做了调查。像美国一样,瑞典也被清晰地划分成了自由派政党和保守派政党。即便瑞典的两派政党都比美国的两派政党更加偏左,但公民也平均分布于这两派政党之间,只有10%的人在接受调查时没有决定自己要站哪队。这项调查包括两党不一致的12个关键议题。譬如:应该增收汽油税吗?瑞典应该重启核能项目吗?调查的主题说明了他们对这个选项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们也表明了自己选举每个政党的可能性,对于自己的观点有多确定,以及对政治的参与度等。
这一调查传递给了每位在键盘前准备投票的网友。这听上去可能只是一个平凡的细节,事实上它却是实验者实行这项恶作剧般的计划的关键。当每一个受访者填写他的答案时,实验者都在观察他,并暗中完成了另一份同样的问卷,这份问卷与他们自己作答的问卷,只有一点细节上的不同:实验者改写了受访者半数问题的答案。当受访者上交完成的问卷时,实验者会在一个笔记本上做一些记录,然后把夹问卷的书写板交回给受访者。但是,通过一个魔术师般熟练的手法,实验者交给受访者的是被改写过的问卷。在对照组,原始问卷又被返还给了受访者。
受访者接下来被要求解释他们为何会对这些问题持此种观点。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被询问:在解释之前是否想要更正或者调整答案?令人震惊的是,在收到了改写过答案的问卷的受访者中,有47%的人根本没意识到任何变化,剩下53%中的大部分人也只是察觉到了一两处变动。只有一个人怀疑实验者改写了他的答案。剩下的人则会说是他们自己误解了这个问题,或者意外地标注了错误的答案。当他们讨论自己的答案时,没有发现自己答案被改写的受访者为自己原本没有选择的答案给出了充分的理由。
这是一种你无法把自己置身于受访者的立场上的实验之一。我们只是无法想象,在人们刚说过希望加税的情况下,如何尝试解释为什么要减税;反之亦然。当然,如果不是参与了这项实验,我们永远不会陷入此类陷阱之中。但是参与这项实验的人有一半跳进了陷阱。他们是否只是出于礼貌而不去修正实验者的错误?若如此,那么把与自己相反的观点当作自己的,就应该对受访者的真实观念没有影响。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实验者要求受访者在研究结束的时候,再一次评估他们有多大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选出一个或两个政党?在对照组,对投票意向的回答与研究伊始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在实验组,受访者明显地向着改写答案的方向,改变了他们的投票意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改写对那些在研究伊始就明确表达了其投票意向的人和那些还在摇摆不定的人的影响同样强烈。这些改写对高度参与政治的人和不参与政治的人的影响也是相同的;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这些改写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即便这个发现令人震惊,但也不能说是反常的。霍尔和乔纳森的团队重复了同样的“花招实验”,他们使用了多种偏好——从道德准则到照片的吸引力等级,再到果酱和茶的口味。在每一项实验中,大比率的受访者(一般是50%~80%)没有注意到答案被改写,继续给那些不是自己选择的答案给出听起来相当合理的理由。
在以上每项实验的最后,实验者透露了原始问卷和被改写的答案,受访者通常都会大吃一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那些他们以为自己坚定持有的信念,原来不过是他们能根据需要而采纳或搁置的支撑点。虽然这些研究并不能完全证明人们缺乏政治信仰,但是至少在一些案例中表明:我们阐述的那些解释我们决定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做出那些决定的真正基础。政治原则是否确实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形成人们观念的基石?此类实验对这个命题提出了怀疑。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原则最多只是形塑政治信仰的一种来源。
当然,这种“心怀叵测”地密谋颠覆我们观念的心理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但只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个人生活的不同侧面,就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布莱恩(Christopher Bryan)与其同事调查了斯坦福大学在校生的政治观点,包括全民医保、单一税率、福利和失业救济金、死刑等自由派和保守派意见相左的议题。然而,在他们完成调查之前,学生们被要求花10分钟来讲讲自己是如何迈进斯坦福大学的。有一半的人只被要求对自己的“努力学习、自律和明智的抉择”发表评论,而另外一半人则只被要求讲讲“机遇和来自他人的帮助”等。要拿到斯坦福大学这种精英大学的入场券,个人品质和外在机遇当然都是需要的,因此两组人马都有着充分的写作素材。
这种在注意力方面看起来很小的转变,导致了政治态度上的巨大差异。相对于考虑好运气的一组,被要求考虑个人品质的一组表达了更保守的观点。抛开他们踏进实验室大门那一刻拥有的意识形态不管,让我们单纯地考量个人品质和机遇在他们各自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 [9] 哪怕仅仅只是这一小会儿。
情感也许会比思想更有力量。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听说2001年9月11日有两架飞机撞毁世贸中心时的情景。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很多非美国人)都清楚地记得他们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时刻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曼哈顿的老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他没事。由于我处于一个相对曼哈顿较早的时区,当我昏昏沉沉地醒来,打开CNN,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在我的记忆中,刚睡醒的懵懂与对整个事件的迷惑交缠在一起。我总在质疑自己当时是否正在做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梦,这使我强化了这样一幅大脑图像——蓝天下冒着烟的白塔。
在这次恐怖袭击过后的几天里,小布什的支持率从51%飙升至90%, [10] 这是总统支持率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数前一天还在反对总统的美国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转变了他们的观点。“9·11”袭击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面临外部威胁。类似地,即便少有人明确讲出,但“团结就是力量”已经被用来记录其他事件了,譬如珍珠港事件和伊朗人质危机。然而,历史证明,比起自由派政府,保守派政府从此类“团结”中会得到更多好处。如果约斯特是正确的——人们接纳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秩序受到威胁的回应,那么在“威胁”与“支持保守主义观念”之间,就应该有特定的联系。
事实上,这个联系有几十年积累的研究支撑。其中有很多研究已经检验了人们的个性与其政治信仰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接一个的实验中,把世界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危险之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那些认为世界比较安全,并常常想要探索和尝试新经验的人,则倾向于更多地支持自由派观点。当然,这些联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考证。譬如,这些感情倾向会像该理论预测的那样,让人们更容易倒向某个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吗?或者说保守派与自由派相对抗的思维方式会让人们切换到不同的情感频道。又或者,这两种思维方式只是反映了导致它们的一些因素。
一些实验开始隔离特定的情感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艾伦·兰伯特(Alan Lambert)、劳拉·舍勒(Laura Scherer)和同事通过给人们展示一个关于“9·11”袭击的视频文件,让他们感到恐慌。与一个只是完成了一些字谜游戏的控制组相比,“9·11”组表达了对小布什总统的支持, [11] 也支持在伊拉克战争中采取更加鹰派的态度,而且更喜欢美国国旗、自由女神像这样的爱国主义符号。心理学家马克·兰多(Mark Landau)和同事要求一组调查对象尽可能生动地想象死亡的样子。兰多和同事指导调查对象仔细描述这种感觉,并设想在他们死后,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与控制组相比,“死亡小组”会有更多的人支持小布什总统, [12] 更少的人支持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研究过程中,克里正在与小布什进行2004年的总统竞选。
田野调查与实验室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9·11”事件后的几年,是美国人最焦虑的几年。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引进了一个恐怖指示系统,用颜色指示提醒民众恐怖活动的风险指数是低(绿色)、增强(黄色)、高(橙色)、严重(红色)。社会学家罗伯·韦勒(Robb Willer)分析了2001年至2004年的总统支持率后发现,无论何时,只要恐怖预警提升,小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提升。 [13] 当恐怖预警减弱时,总统支持率就会随之下降。恐怖指数日复一日的升降牵引着我们的意识形态!
我们通常会谈到保守派和自由派,而不是“保守的时刻”和“自由的时刻”。其实两者我们都经历过。有时我们会基于自己的原则考虑问题,最终得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结论。有时我们会从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得到提示,并发现一种适合这个时刻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出反应时,想要分辨出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近期记忆中,在所有把我们在左右之间推来推去的因素中,财富、贫困和不平等扮演的角色是最令人头疼的话题之一。我们的文化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在政治上有何不同的叙述并不一致。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两种迥异的个体人生。
厄尔是卡车司机,而且大部分时间开长途车,譬如拉着前装载器和挖掘机从莫非斯堡开到韦恩堡。晚上回家后,他喜欢边喝啤酒边看当地新闻。在周末,他会观看“纳斯卡”(NASCAR,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的比赛。一旦错过一场比赛,他就会查阅报纸上的车手排名和快递过来的宣传册。除此之外,他也没啥爱好。当他最小的孩子离开家后,他觉得自己应该收拾收拾园艺了,但是他的周末时光大部分用来修理他的老房车。厄尔在肯沃斯钻井平台赚到的钱远比待在家里要多。虽然他在卡车里很少会用到卧铺舱,但它永远是在家里屋顶坏掉后首选的容身之地。
大卫今年已经换了三个园艺师了。第一个不太可靠,第二个总是用割草机砍掉草坪喷灌器的喷头。现在他的草坪最终被修剪成了与他在道路尽头新建的房子相配的样子。他喜欢把这栋房子说成是自己设计的,但设计师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安德莉亚,她只不过照搬了建筑家装杂志中选出的别人设计的成品而已。他们为这栋房子攒了五年的钱,希望它是完美无缺的。这栋房子有四间卧室和一间办公室,他们晚上经常在家中办公。还有一间健身房,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时练瑜伽和在运动器械上健身。但最令他们骄傲的还是遮阴的门廊,清晨,他们会用大卫的最新式虹吸壶喝咖啡,这种壶通过一系列玻璃管将水吸上来,看上去就像19世纪的实验装备一样。在啜饮咖啡时,大卫会在手机上看新闻,而安德莉亚则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最近,他们一直在讨论为退休后的生活投资更多项目。
令人惊叹的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人们生活的小侧面来区分他们呢?在以上简短的介绍之后,你是否感觉到自己了解了厄尔和大卫生活的其他方面呢?譬如,谁更有可能出去吃一顿寿司?谁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基本靠吼,而谁会走到在另一间屋子的家人身边小声说话?谁会为送孩子去读哪所学校而苦恼几个月?
如果你得知厄尔是一个重生基督徒,而且反对同性婚姻;但大卫认为同性恋人群可以结婚,你是否会感到诧异?当你发现大卫支持限制持枪权的法律,而厄尔却支持全国步枪协会时,或者说厄尔更倾向于“小政府”并认为应该削减所得税时,可能也并不奇怪。
你当然知道答案。在我们的头脑中,关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应有的形象,已经被渲染得十分详尽了,它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保守派开着一辆敞篷小型载货卡车,车里放着乡村音乐,载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可以再想象一下,自由派从农贸市场出来,开着普锐斯回家,车里放着大卫·赛德瑞斯的广播节目,还得小心翼翼地别在路上把他们的传家宝番茄弄坏了。你甚至可以通过他们的消费模式来区分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由派开着路虎和雷克萨斯,而保守派更喜欢开庞蒂亚克和别克。自由派喜欢喝山姆·亚当斯轻啤,而保守派则喜欢喝百威啤酒。自由派在帕尼罗面包店吃羽衣甘蓝沙拉,而保守派在克莱克·拜瑞尔乡村餐厅吃炸鸡排。
自由派精英和工薪阶层的保守派之间的这些差别看上去也会反映在他们的投票模式上。举个例子,你觉得厄尔还是大卫更有可能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呢?自由派精英和工薪阶层的保守派之间的这些差别带来一个大难题。就像许多作家声称的那样,人们似乎会投出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反的票。少有富裕的保守派会把票投给颁布主要让富人受益的减税令而削减帮助穷人的政府福利的领导人。托马斯·弗兰克的畅销书——《堪萨斯到底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 [14] 提供了对这个悖论的一种解释:一小部分共和党富裕精英通过“上帝、枪和同性恋”等热点问题来激怒美国工薪阶层,让他们给支持富人的政策投票。这些文化上的议题会引起强烈的愤怒。这个理论认为,人们会给并不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投票。
在小布什再次当选之后,《洋葱报》(The Onion )这家讽刺网站,在一篇题为“这个国家的穷人为这个国家的富人赢得了竞选” [15] 的文章中,精辟地总结了这种观点:
“共和党——工业大资本家、公司金融家、权力掮客和富裕精英的政党——会感谢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乡下穷人、在美国中部挣扎生活的蓝领工人和虔诚的、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少数族裔,他们才是把小布什抬回总统办公室的人。”小布什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在周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您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福祉,而投给了有损自己经济利益的一方。就冲这一点,我们诚挚地感谢您!”罗夫还说:“您的行为超出了职责的范畴,这是使命的召唤!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您有眼光!”
问题是这整个论述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它不仅仅是错误的,几乎可以说是拉了历史的倒车。
很显然,大部分穷人给保守派投票,而大多数富人给自由派投票这种事并不存在。事实上,一个人的收入越高,他就越有可能投给共和党。全部人口中最富有的1/3比处于中间的1/3给共和党投的票更多,而中间的1/3给共和党投的票又比最穷的1/3更多。
政治学家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已经用数据证明了这些趋势,这些数据来自《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Studies)和《国家安娜堡选举调查》(National Annenberg Election Survey)以及全国与各州的投票后民调。这些调查尽力保证它们能够代表美国人口,而且它们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即便没有一个收入群体是铁板一块的,以下趋势也是很明显的:越富的人越有可能把自己当成共和党的信徒, [16] 从而给共和党投票;越穷的人则越有可能把自己当成民主党人,从而给民主党投票。
让我们来看看图4.2展示的这张2004年总统选举地图。给小布什投票的州被标记为深色,给约翰·克里投票的州被标记为浅色。这是我们对贫富选民的错误认知的来源之一。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样富裕的海滨州,我们看到的是安静地酌饮拿铁咖啡的自由派。在美国中部那一大片深色的贫困州,我们视之为穷人、虔诚的保守派的故乡。但是正如格尔曼指出的那样,对各州所处层次的这些总结,忽略了在这些州中的个人收入情况。如果我们用选民的收入分解投票统计,就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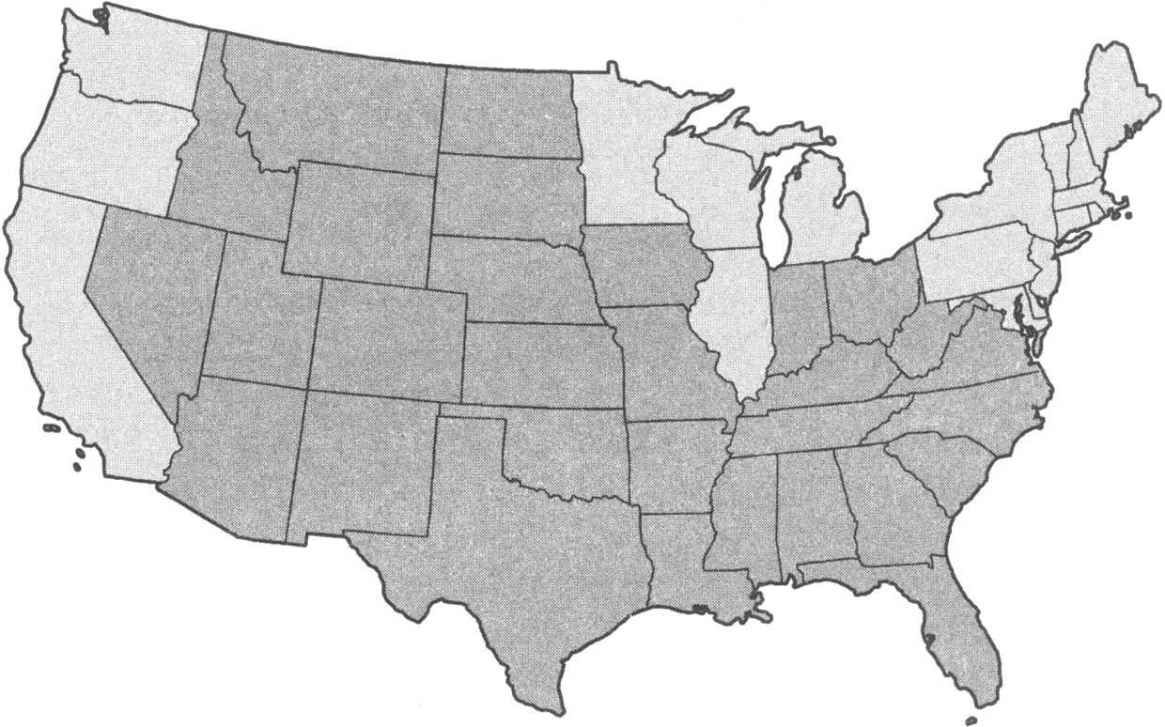
图4.2 2004年总统选举地图
注:深色州表示该州是共和党胜利,浅色州表示该州是民主党胜利。
资料来源:Gelman(2006)。
图4.3展示的也是2004年的选举地图,不过它是基于选民本身的收入而重绘的。上图展示的是只把穷人的票数计算在内的选举地图——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下图展示的是只把富人的票数计算在内的选举地图——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金钱对选举地图的影响与我们对红色和蓝色阵营的刻板印象相反。
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品位和风格有何不同?竞选广告主花了很长时间去收集每个党派的支持者的消费喜好数据。 [17] 他们发现路虎和雷克萨斯是两个“共和党”的汽车品牌。举个例子,路虎汽车的拥有者中,支持共和党的人比支持民主党的人多出30%。相比之下,民主党支持者则更偏向庞蒂亚克和别克。你也许会感到惊讶的是:雪佛兰、福特和沃尔沃的拥有者在党派间是平均分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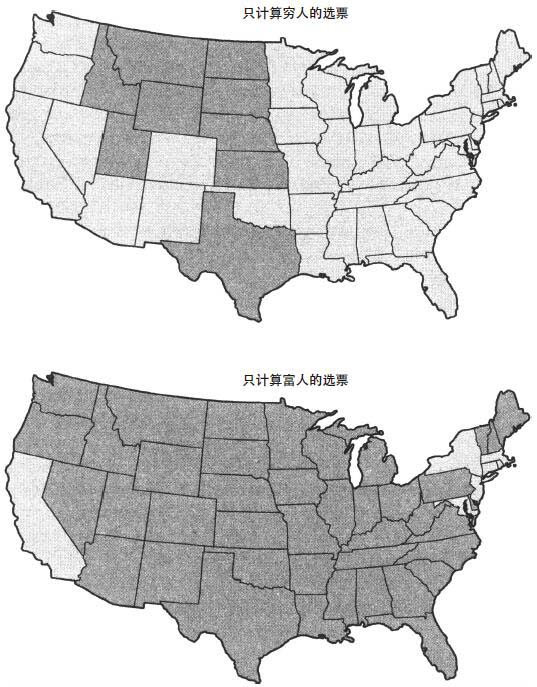
图4.3 如果我们只只计计算算富穷人人的(选上票图)和富人(下图)的选票,2004年总统大选的选举地图就会是这个样子
注:深色州表示该州是共和党胜利,浅色州表示该州是民主党胜利。
资料来源:Gelman(2006)。
对政治偏向者用餐习惯的刻板偏见也被发现是错误的。克莱克·拜瑞尔和帕尼罗面包店吸引了更多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显然更喜欢金克拉尔(Golden Corral)、唐恩都乐(谁知道呢?)。我们甚至把两党人士青睐的啤酒品牌都弄错了。与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共和党人喜欢山姆·亚当斯轻啤,而大部分百威啤酒都被民主党人喝掉了。我们喝拿铁逛农贸市场的自由派,也许会感到惨不忍闻:最“民主党”的啤酒是“密尔沃基优选”(Milwaukee's Best)。最“共和党”的啤酒甚至不是美国酿造的,而是从荷兰进口的阿姆斯特尔轻啤(Amstel Light)。
基于政治偏好的消费模式并不总是错误的。民主党人的确买了大部分的普锐斯汽车,而看福克斯新闻的也确实多为共和党人。但是这些品位的表达与两党成员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直接相关的。人们选择普锐斯的原因是他们关注气候变化。人们看福克斯新闻是因为它提供了他们喜欢听到的右翼观点。然而,当我们从实际的政治议题上走得更远时,我们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印象就会变得更加薄弱,更容易流于空洞的刻板印象,从而对我们产生误导。
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自由派社会精英和保守派社会中坚标准概念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比较陌生,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格尔曼构建的模型也有同想。世界上的每个资本主义经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竞争、市场监管和税收。它们都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没有严肃的左派或右派思想家会认为你可以与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完全割离开来——接近百分之百的税率一定会扼杀激励和创新;中央计划经济在20世纪的转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政府集中调控和征税不能与自由市场经济体相抗衡的证据。而完全无调控的市场则是另一个极端,它很快就会导致垄断,违背市场竞争的初衷;税收不足则会导致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军事防御状况的恶化。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存在于以上极端情况之间的中间状态。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调控,有的是以税收,有的则为底层民众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安全网。如果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关于经济的辩论看作一个针管,那么双方的最终指向都是试图把针管的活塞向对方推进一点。保守主义政策意在提升自由市场,而自由主义政策则寻求更多的税收以支持共享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项目。
经济学家曾声称:近几十年来,理性的政治选择(理性在此被狭义定义为自我利益)依赖于你有多少钱。当谈到共享的基础设施,譬如道路和军事防御等议题时,每个人都同样从中获利。但是安全保障项目对穷人的帮助则比富人更多,因此,你挣的钱越多,你就越会支持低税收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你挣的钱越少,你就越有动力支持高税收和财富再分配。在这个框架下,人们的行为看上去符合经济学家对于理性的想象,使用基于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计算工具做出决定。
在你预估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之前,他们的行为看上去都是与这个模型相符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调查了那些接受不同政府福利的人。他们向受访者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曾经接受过某项政府的社会项目吗?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有一半人认为他们从未接受过。举例来说,在接受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人中,有40%拒绝承认享受过政府福利。同样,在获得所得税减免的人之中,有47%的人也做了同样的声明。有一半以上接受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的人说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政府福利。这些受访者并不是在撒谎。譬如说,联邦医疗保险的接受者会承认自己接受了社会医疗,不过他们不认为这与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政府项目是否有利于他们的个人经济利益并没有概念。 [18]
人们也许并不能理解政府福利的范围,那么他们能意识到对其更有利的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税收吗?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调查了人们对减税之与其自身利益的了解程度。呈现其研究成果的文章的标题完美总结了他的答案:“荷马得到了减税。” [19] [02] 巴特尔斯研究了美国人对小布什政府通过的减税政策的看法。这些措施产生的主要后果高达上万亿美元。而且,当这些人们被问到他们是支持、反对这次减税,还是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时,40%的回应者说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被问到关于这次减税以及对他们产生的后果这类实质性问题时,大部分人不是不知道答案,就是答错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政治新闻迷。因此,巴特尔斯尝试判定:如果人们在总体上对政治的认知程度更强,他们是否可能对减税的认知程度也更高。这项调查包含一个由七道小问题组成的测验,以衡量回答者对这个话题的熟悉程度。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难。例如,其中一道问题是,当时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持什么立场;另一道问题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是谁。对政治有充分了解的人,对减税也了解更多。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属于这一类。绝大多数受访者答错的题比答对的多。如果这份调查问卷是一场课堂测验,那么大部分美国人都会挂科。
普通美国人如何能够以一种对自己经济上有利的方式投票呢?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其中一条线索来自“感到贫穷”的力量;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感觉也并不只是依赖于人们自己的财富。格尔曼对投票与收入的研究为相对比较的重要性提供了线索。贫困州的富人投共和党的倾向比富裕州的富人更强。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密西西比人,你就比同样富裕的纽约州人或康涅狄格州人更有可能投共和党的票。尽管原因还没完全弄清,我推测它应该与在贫困州或富裕州的人之间不同种类的相对比较有关。如果你在比洛克西(Biloxi)年薪20万美元,那么很容易就会比你身边的大部分人感到更富有。但是如果你在曼哈顿挣同样的收入,就会觉得自己只是中产阶级。
我和我的同事猜想,社会比较对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影响也许会比对其实际财富的影响更大。我们聚焦于经济学家声称的与一个人自身经济利益明确相关的政策,即税收和财富再分配。为了检验这个想法,我们开始改变人们的社会比较,以观察其政治观点是否也会随之变化。我们要求一组参与者在线上回答一个关于他们的收入、消费习惯、购买品位甚至个人特质的长期跟踪调查,然后给他们提供线上反馈。尽管参与者认为这个反馈是基于他们对调查的回答,实际上,我们只是随机派发了我们准备的两种反馈中的一种。第一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比大部分与之在人口统计学和个性上差不多的人更有钱;另一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比大部分与他们相当的人更没钱。然后,我们询问了这两组参与者一系列有关政治议题的问题,包括税收和再分配。
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觉得自己相对富裕的参与者不太支持再分配,而那些觉得自己相对贫穷的参与者更加支持再分配。其实这两组参与者的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水平都一样。而让一切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到底比同辈更富还是更穷。社会比较导致了政治观念上的差别。 [20]
这项调查同样指出,民众总体上可以依据其经济利益投票,除非他们被错误地告知其利益所在。想象一下,感觉自己比平均水平强的人投票给减税和削减福利津贴,而那些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差的人投票给加税和增加福利津贴。因为相对地位的感觉是(适度地)与实际收入相联系的,人们对自身利益有正确判断的时候比错误判断的时候多。平均来说,个人随机投票模式与基于自利的投票模式类似。就像椋鸟的群移一样,成百上千万在与邻居相比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上目光短浅的人,也能形成一个看上去是为了特定目的而移动的群体。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倾向于给他们感觉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投票,而不管这些政策是否真正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符合自身利益的感觉取决于他们如何与他人比较。当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隔阂加剧,我可以想见,社会比较的效果会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些观察共同揭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平等的扩大可能导致日益激烈的党派偏见和政治冲突。
如今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政治在近些年变得更加极端化。这种观察是有数据支撑的。地球科学家克莱奥·安得里斯(Clio Andris)和她的同事运用了绘制地理距离的数据分析技术,基于投票表决名单绘制了美国众议院不同党派成员间的“距离”。无论何时两个代表以同样的方式投票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比较接近。当他们的投票结果不同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被拉远。结果令人震惊。
图4.4展示了1981年、1991年、2001年和2011年每个国会代表之间的距离。每个众议员都用一个黑点(共和党人)或一个灰点(民主党人)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重叠的地方很多。许多灰点与黑点的区域重合,颜色就更深了,许多黑点也与灰点的区域重合。两者之间的边界是稀疏的、可互相渗透的。然而,每过10年,重叠部分都会减退。到了2011年,双方几乎都与对方完全封闭起来,而且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成了真空地带。这些直观化的信息生动地描述了过去40年来分离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趋势。 [21] 不平等是否加剧了这种分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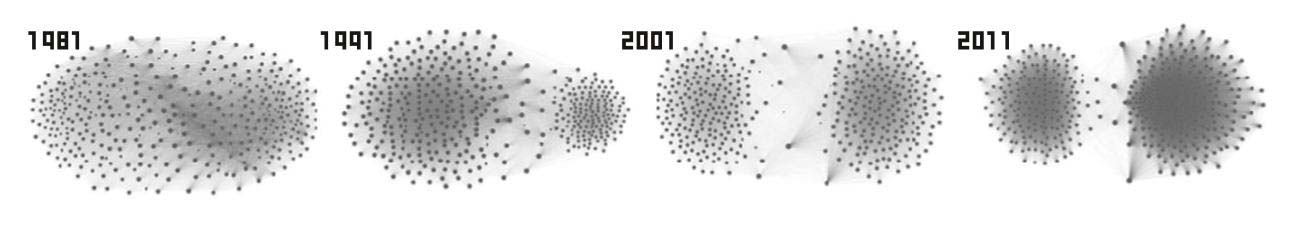
图4.4 美国国会两极化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Adris et al.(2015)。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实验室。我们开展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参与者被给予了一些股票。他们阅读了与该股票相关的每家公司的资料,包括公司市盈率及公司股票在最近6个月的表现。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利用实验者发给他们的启动资金,采取任何股票组合方式进行投资。实验参与者被告知,股票的市场表现基于过去6个月的实际市场表现模拟,而且他们可以保留自己从这些投资中获得的所有收益。在现实中,每个人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了30%的利润,但是其中有一半参与者被告知自己的表现优于其他89%的人,而另一半人则被告知自己的表现不如其他89%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实际收入没有任何差别的情况下,制造了相对地位的差别。
两极分化的演化是这项实验的关键部分。我们现在告诉参与者的规则是根据之前参与者的投票制定的。其中一项规定是:高收入者会被征收20%的所得税,以补偿低收入者的损失——低收入者会收到20%的奖励。换句话说,这个游戏包含了一种再分配的政策。为了发现相对地位是否会改变人们对再分配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要求参与者就如何改变未来活动的规则进行投票。正如我们基于相对地位的作用做估计那样,处于高位的群体希望减税并减少再分配,而处于低位的群体则希望加税,并为未来的参与者增加福利。
接下来,我们为实验对象展示了另一位参与者在建议,这位参与者在再分配问题上要么同意、要么反对实验对象的建议,并询问他们对这一参与者的评价。这“另一位参与者”的能力究竟如何?他有没有受“原则”指引,或者带有“自身利益”的偏见?再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游戏的规则呢?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还是一个非理性的傻瓜呢?
正如我们所料,当“另一位参与者”与实验对象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会被认为更没能力、更差劲、偏见更重、更缺乏理性。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数据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对这位充满偏见且非理性的“另一位参与者”的感知,完全是由被告知自己比其他同僚强的那组人驱使的。利益上的优越感使人们觉得自己在观念上也比其他参与者要先进。
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人是聪明且富有洞见的,而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需要一些帮助才能看清事实真相。就像乔治·卡琳(George Carlin)所说的那样:“你是否注意过,你觉得所有比你开车慢的人都是白痴,而所有开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疯子?” [22] 自认为能够准确地认识世界,而将持异见者视为愚昧无知的倾向会加剧冲突。正如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所说:“如果我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只能用几种可能性来解释你的行为——你也许是无能的,也许是非理性的,你还可能是邪恶的。” [23] 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是不可理喻的。
如果这些感知上的差异在自我感觉富裕的人之间尤其严重,那么我们就会在不平等持续攀升的时候面对一些令人烦恼的暗示。当收入顶端的少部分人与处于底层的广大工薪阶层距离越拉越远时,可以想见他们的政治观点差异会更大。顶层人群会错误地把其自身利益当成普遍原则,而且他们会以一种蔑视的眼光看待与他们观点相左的人。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政敌看作是无能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不道德的,那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妥协。
为了证实感觉富裕是否确实有影响这些信念的潜力,我们用投资游戏做了一项终极实验。像以前一样,每个人选投股票后都获得了同样的利润,但有一组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好,另一组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差。我们给这群投资者展示了另一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他们的“第三者”关于再分配的建议。然而这一次,除了询问实验对象如何看待这位第三者之外,我们还告诉他们这位第三者将参与到为未来参与者制定规则的投票之中,而且他的投票会跟其他人的投票占有同等的比重。然而,他们能改变的规则之一,就是每个人的投票是否都会受到同等对待。
实验结果发人深省。跟以前一样,觉得自己的收入比较低的实验对象希望加大再分配。但是他们希望每个人的投票都受到同等对待,不管这位“第三者”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收入较高的实验对象则想要减少再分配,而且他们投票反对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投票。 [24] 他们越觉得这个“第三者”无能、非理性,就越不希望他投的票算数。这项研究首次表明,地位优越感会放大我们的感觉,即当我们的对手受到蒙蔽时,我们能看清现实。它支持了如下观点:当社会阶梯顶部和底部之间距离越来越大时,政治就会更加分裂。过去几十年的情况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
政治学家诺兰·麦克卡迪(Nolan McCarty)和他的同事也追踪了20世纪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政治决议,形成了一个基于立法者如何投票的极化现象的衡量尺度, [25] 与安德里斯图表所用的数据差不多。当所有民主党人以一种方式投票,同时所有共和党人以另一种方式投票时,这个极化指数就会达到最高点。使用这个指数,他们计算出了美国政治在1947年之后的每届国会中是如何走向极化的。图4.5展示了众议院的极化现象和基尼系数之间遵循着惊人相似的轨迹。参议院的情况也类似。不平等和极化水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相对较低。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同步上升,并始终保持着同一水平。
行为实验和历史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经济领域出现分歧,政治领域同样也会出现分歧。人们越来越难以把另一阵营的人看作与我们目标一致,只是在达成目标的最佳方式上意见不同的好人了。于是,另一阵营的人看起来就越来越像是敌人。
莱斯利·拉特利奇(Leslie Rutledge)是阿肯色州的首席检察官。当她在2014年当选时,为了一张选票——她自己的,不得不比预想中付出更多努力。拉特利奇是一名共和党人,她支持阿肯色州2013年的身份证法案, [26] 这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他们的身份证件。民主党人反对这项法案,因为它毫不掩饰地阻止更不可能持有有效证件的穷人和少数族裔投票。共和党人声称这种在投票箱旁设置的严格标准,是重要的防作弊手段。阿肯色州的法律还要求公民若想投票,必须在本州登记,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登记。因此,当民主党县职员拉里·克拉内(Larry Crane)看到拉特利奇还在她曾经居住过的华盛顿特区登记时,就取消了她的投票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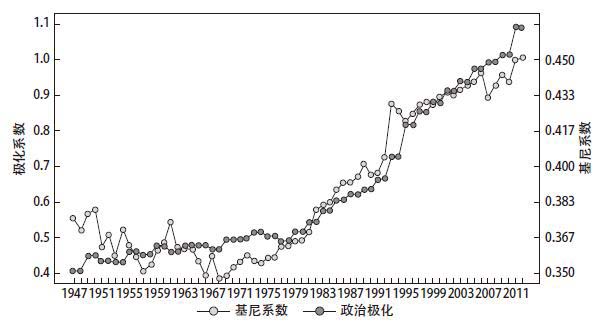
图4.5 1947—2012年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极化
资料来源:Ma Carty、Poole and Rosenthal(2016)。
拉特利奇指控克拉内用“芝加哥式的政治”剥夺了她的选举权。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幸灾乐祸了几天,并写了许多博客文章探讨“讽刺”的真正含义。
你如何看待阿肯色州共和党人通过投票身份证法案的真正动机?你觉得克拉内阻止拉特利奇投票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姑且不论这个案例中谁对谁错,你更可能确信自己正在清晰地评估局势,而那些与你意见相左的人,往好里说是有意忽略,往坏里说就是居心不良。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普通美国人中,对反对党持“极不同意”观点的比例在近30年中稳步上升,与此同时,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在2014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反对党成员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对国家福祉的威胁。 [27] 三分之一的保守派和四分之一的自由派说,如果他们的家庭成员与对立的党派成员结婚,会令自己感到沮丧。这些趋势是危险的,因为当“反对者”变成“敌人”时,人们可以通过反驳来证明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有理。毕竟,你怎能期望与白痴和疯子讲理呢?
[1] M.Gauchet,“Right and Left,”in Realms of Memory: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P.Nora and L.D.Kritzman(ed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241-99.
[01] 格伦维尔男爵(Baron de Gauville),这里指的是第一代格伦维尔男爵——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1759年10月25日—1834年1月12日),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在小威廉·彼得逝世后继任为首相,但是,由他组织而成的政府最后因为内部出现意见分歧而倒台,所以,他任首相不足一年半。他执政期间,未能成功结束对法战争,也未能成功为天主教徒争取权利,不过,他在这段时间里,引入了1807年《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 1807),废除了奴隶贸易。——译者整理自维基百科
[2] J.T.Jost,C.M.Federico,and J.L.Napier,“Political Ideology:Its Structure,Functions,and Elective Affinities,”Annual Review ofPsychology 60(2009):307-37.
[3] H.Hildenbrandt,C.Carere,and C.K.Hemelrijk,“Self-Organized Aerial Displays of Thousands of Starlings:A Model,”Behavioral Ecology 21(2010):1349-59.
[4] R.Wilbur,“An Event,”in Collected Poems,1943-2004(Orlando,FL:Harcourt,2004),347.
[5] S.G.McFarland,V.S.Ageyev,and M.A.Abalakina-Paap,“Authoritarianis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1992):1004-10.
[6] A.C.Kay and R.P.Eibach,“The Ideological Toolbox:Ideologies as Tools of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in The SAGE Handbook ofSocial Cognition,S.Fiske and C.Macrae(eds.)(London:Sage,2012),495-515.
[7] R.E.Nisbett and T.D.Wilson,“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Psychological Review 84(1977):231-59.
[8] L.Hall et al.,“How the Polls Can Be Both Spot On and Dead Wrong:Using Choice Blindness to Shift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oter Intentions,”PLOS ONE 8(2013):e60554.
[9] C.J.Bryan et al.,“Political Mindset:Effects of Schema Priming on Liberal-Conservative Political Positions,”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2009):890-95.
[10]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George W.Bush,”Gallup,www.gallup.com/poll/116500/presidential-approval-ratings-george-bush.aspx.
[11] A.J.Lambert et al.,“Rally Effects,Threat,and Attitude Change: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mo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2010):886-903.
[12] M.J.Landau et al.,“Deliver Us from Evil: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and Reminders of9/11 on Support for President George W.Bush,”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2004):1136-50.
[13] R.Willer,“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ssued Terror Warnings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10(2004):1-12.
[14] T.Frank,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America(New York:Macmillan,2007).
[15] “Nation's Poor Win Election for Nation's Rich,”The Onion,November 10,2004,www.theonion.com/article/nations-poor-win-election-for-nations-rich-1246.
[16] A.Gelman,Red State,Blue State,Rich State,Poor State:Why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7] “New Study Reveals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Disagree on the Brands They Love Most,”retrieved from buyology.com.
[18] S.Mettler,The Submerged State:How Invisible Government Policies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19] L.M.Bartels,“Homer Gets a Tax Cut: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American Mind,”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2005):15-31.
[02] 拉里·巴特尔斯的论文标题为“荷马得到了减税:美国人心中的不平等与公共政策”,“荷马”指的应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座小城荷马,这座城市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拥有游艇。在这篇文章中,巴特尔斯认为人们对自身利益是不自知的。——译者注
[20] J.L.Brown-Iannuzzi,K.B.Lundberg,A.C.Kay,and B.K.Payne,“Subjective Status Shapes Political Preferenc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6(2015):15-26.
[21] C.Andris et al.,“The Rise of Partisanship and Super-Cooperators in 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PLOS ONE 10(2015):e0123507.
[22] G.Carlin,B.Carlin,and S.J.Santos,Carlin on Campus(MPI Home Video,2001).
[23] R.J.Robinson,D.Keltner,A.Ward,and L.Ross,“Actual Versus Assumed Differences in Construal:‘Naive Realism’in Intergroup Perception and Conflict,”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1995):404-17.
[24] J.L.Brown-Iannuzzi,K.B.Lundberg,and B.K.Payne,“Subjective Status Increases Naïe Realism,”Working Paper,2016.
[25] N.McCarty,K.T.Poole,and H.Rosenthal,Polarized America:The Dance of Ideologyand Unequal Riches(Cambridge,MA:MIT Press,2016).
[26] M.Campbell,“Leslie Rutledge's Voter Registration Canceled;Candidacy Now in Doubt,”Blue Hog Report,September 30,2014,www.bluehogreport.com/2014/09/30/breaking-leslie-rutledges-voter-registration-canceled-candidacy-now-in-question/.
[27]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Pew Research Center,June 12,2014,www.people-press.org/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10月底的老教堂山墓地,我跪在一块深陷于泥土中的小石板前,拂去其上的落叶——“珀西·R.贝克,1913年6月23日—1966年5月11日”,再多活几周,他就53岁了。在几英尺外,一个饭盒大小的标记牌半掩在灌木丛中,上面的文字让我心中一惊——“小托马斯·W.巴特尔,1918年3月15日—1918年5月10日”。
墓地的另一边耸立着一块立式钢琴大小的壮观石碑,碑文字体很大,在几码远之外都能看到,上面写着:“威廉姆·F.斯托德,1832—1911”。纪念文字大约讲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也是北卡罗来纳州制宪会议成员,美国国会议员。斯托德活到79岁,这个岁数在平均寿命只有51岁的年代还是很少见的。一块比一人还高的方尖碑矗立在旁,黑色花岗岩上刻着金色的盾形徽章,十分奢华,上书“尤金·辛普森和玛格丽特·辛普森之墓”,他们分别活了79岁和85岁。
我不认识贝克、巴特尔和辛普森的后代,让我去实地考察的原因是我最近读到了一篇结论十分奇特的研究。该研究声称,你可以通过墓碑的大小来预测墓碑上铭刻的主人的寿命。简而言之,就是财富决定论。你越富有,你的寿命就越长,你的家族也就能负担得起更大的墓碑。寿命长短和墓碑大小之间的关系被一位名叫乔治·大卫·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的苏格兰流行病学家记录了下来。乔治的团队走遍了格拉斯哥的墓地, [1] 将所有墓碑的高度和墓碑上铭刻的生卒年月记录在册。他发现,墓碑的边长每多一米,寿命平均就会长上两年多。我带着本科班的学生来到校园墓地,用卷尺丈量这些墓碑,以检验是否能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现相同的规律。果然,我们在教堂山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更大的墓碑的主人寿命也更长。
当然,对于贫穷为何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很多种解释。譬如穷人可能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护理,缺少安全的生活环境以及良好的卫生条件,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死于饥饿等。而更普遍的情况是,营养不良的孩子难以发育出健康的免疫系统,像麻疹那样常见的感染都有可能导致他们死亡。这两种死因共同构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统计数字——每8秒钟就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或者10秒,或者15秒,随着过去10年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这个令人痛心的数据也在下降)。在图5.1中,你可以看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寿命差异。 [2]
当我们检视单个国家的数据时,在金钱和健康之间的关联也非常明显——你的财富越多,你的健康状况就越好,你可能活的时间也越长。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最富有和最贫困的州之间在死亡率上的差别。在最富有的州,每年的死亡率约为5‰;在最贫困的州,死亡率几乎翻倍,达到9‰。财富上升的每一步都会转化为生命的延长。
从一项针对一万多名英国公务员的大型研究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模式, [3] 这项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
女王陛下的公务员队伍有着十分细致精密的等级制度,包括几十个定位明确的工作职级——上至直接向首相汇报的内阁部长,下至入门级的办事员。迈克尔·马尔默特(Michael Marmot)医生发现,公务员的职级每下降一级,寿命就相应缩短一些。这种模式呈现如此显著的线性关系,以至于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和那些只比他们低一级的官员之间也存在着死亡率递增的情况(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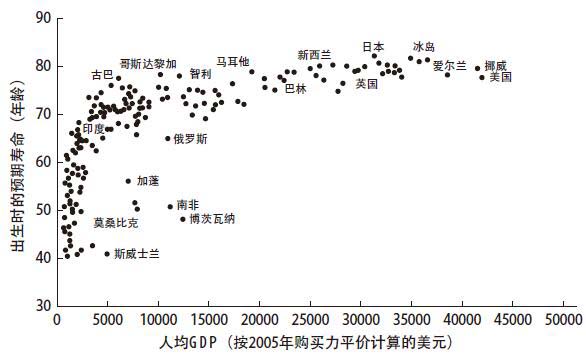
图5.1 当国家达到基本的发展水平后,人均收入对寿命的影响曲线趋于平缓
苏格兰的墓碑研究中还包含了一个生动的细节,进一步阐明了财富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史密斯提到,他们研究的大多数墓地都属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人士(穷人通常没有墓碑就下葬了,或者只是用一块木头标记一下,这种东西不会保存很久)。这个特定的事实听起来很重要,但是它为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即财富如何影响健康,提供了研究的线索。
在“银色马”的故事中, [4] 福尔摩斯调查比赛前夜驯马师被谋杀、明星赛马失踪的案件。一位伦敦警察厅的侦探问福尔摩斯:“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问题吗?”福尔摩斯回答道:“还有狗,在案发当晚狗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当晚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侦探回答道。福尔摩斯答道:“这正是最奇怪的事情。”当晚狗没有叫,说明这个偷马贼一定来自内部,和狗十分熟悉。福尔摩斯发挥了超凡的智慧,注意到了证据缺失正是证据所在。对于科学家而言,他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在发达国家的财富和寿命关系的曲线图中,有一些东西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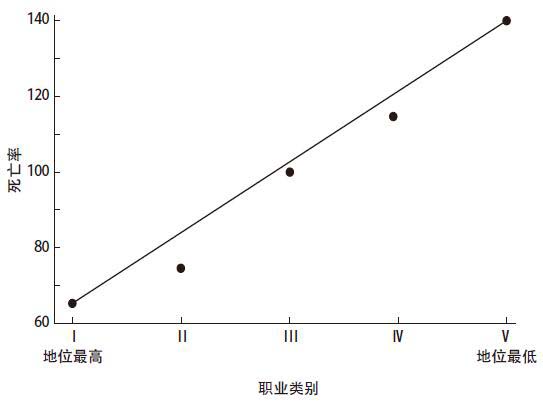
图5.2 在富裕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死亡率呈线性相关
资料来源:Marmot's study of British civil servants(2004)。
如果你仔细观察图5.1,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对比曲线是弯曲的。举个例子,印度与莫桑比克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收入优势,但它却转化成了较大的寿命优势。当国家一旦发展到智利或者哥斯达黎加的水平时,有趣的事情便发生了:这条曲线开始变得平缓。像美国这种极富有的国家,对比那些中等富裕的国家,例如巴林,甚至古巴,都不再有任何寿命优势。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平均收入的增加对寿命不再有显著影响。
但是,在一个富裕国家内部,这条曲线是不会弯曲的;财富和寿命之间依然是线性相关的。如果这种相关性是由极贫困人口的高死亡率所致,那就会出现弯曲。也就是说,你可以设想极贫困人口会有极其短暂的寿命,而一旦超过贫困线,多余的收入对寿命长短的影响甚微。曲线图中弯曲部分的离奇缺失表明,财富和健康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反映贫穷本身,至少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不是这样。如果这种效应是由极端贫困所致,那么极贫困人群会出现死亡率的高峰,而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人群之间的死亡率则相差无几。
英国公务员研究中的线性模式同样显著,因为这一研究中的研究对象都有着体面的政府工作,有工资、医保、养老金和其他相关福利。如果你认为死亡率的提升仅仅是由于极度贫困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而造成的,那么本研究不支持该观点,因为本研究中不包含任何极度贫困的研究对象,但我们依然在较低阶层的人群中发现了死亡率的上升。
心理学家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和她的同事发现,人们对自己在社会阶梯中所处位置的认知,是比其实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更合适的健康指示器。 [5] 事实上,在同马尔默特的合作中,阿德勒团队重新拾起了对伦敦公务员的研究,要求研究对象衡量自身在社会阶梯中的位置。
在发达国家,如果健康长寿与否和人们之间相对比较的关联更紧密,而与人们纯收入的关联较小,那么可以推测生活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健康水平就会更差。事实也的确如此。威尔金森和皮科特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收入更均衡的国家,人们的预期寿命更长(图5.3)。 [6] 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收入更加均衡的州人们的寿命更长(图5.4)。当我们在统计上控制平均收入时,以上两种关系依旧成立,这表明对寿命起决定作用的是收入不平等,而非收入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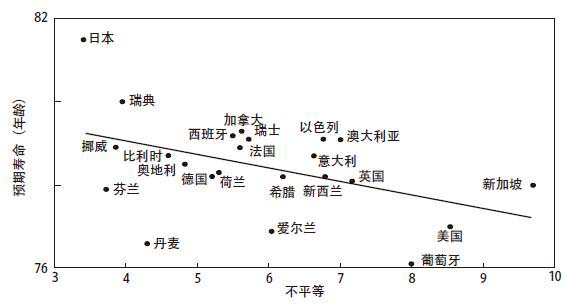
图5.3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更高程度的不平等与更短的寿命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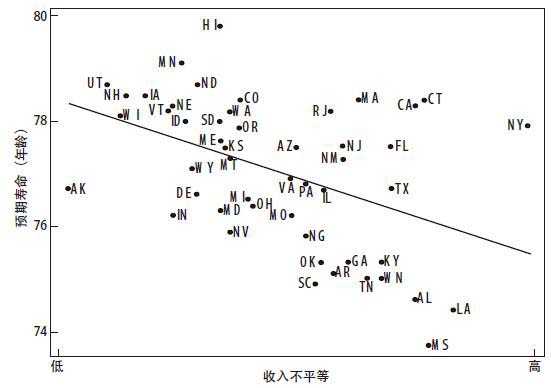
图5.4 在美国,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州,人们的预期寿命更短
注:亚拉巴马AL、阿拉斯加AK、亚利桑那AZ、阿肯色AR、加利福尼亚CA、科罗拉多CO、康涅狄格CT、特拉华DE、佛罗里达FL、佐治亚GA、夏威夷HI、爱达荷ID、伊利诺伊IL、印第安纳IN、艾奥瓦IA、堪萨斯KS、肯塔基KY、路易斯安那LA、缅因ME、马里兰MD、马萨诸塞MA、密歇根MI、明尼苏达MN、密西西比MS、密苏里MO、蒙大拿MT、内布拉斯加NE、内华达NV、新罕布什尔NH、新泽西NJ、新墨西哥NM、纽约NY、北卡罗来纳NC、北达科他ND、俄亥俄OH、俄克拉何马OK、俄勒冈OR、宾夕法尼亚PA、罗得岛RI、南卡罗来纳SC、南达科他SD、田纳西TN、得克萨斯TX、犹他UT、佛蒙特VT、弗吉尼亚VA、华盛顿WA、西弗吉尼亚WV、威斯康星WI、怀俄明WY
资料来源:The Spirit Level(2009尔),第83页。
那么,像不平等和人际攀比这种抽象的事物,是如何对身体健康这种具体事物产生实际影响的呢?急诊室里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没听说谁是患了“严重不平等”的病。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某些特定疾病,发现不平等与健康的关联途径,尤其是心脏病、癌症、糖尿病以及肥胖引发的健康问题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关系等抽象概念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细胞机能上体现出来。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人之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死法,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如果人们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的州和国家,在暴力倾向、婴儿死亡率、肥胖和糖尿病、心理疾病等许多方面的健康测评结果更差。在第三章中我们了解到,不平等驱使人们冒更高的风险,不确定的未来导致人们选择冲动的“快生早死”的生活方式。受到享受眼前欢愉的诱惑而抛弃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健康,这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联。在极端不平等的地方,人们滥用毒品和酒精、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等情形的概率更高。也有其他研究表明,生活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会增加人们吸烟、暴饮暴食和缺乏锻炼的概率。
综上所述,这些证据表明——不平等之所以导致疾病和短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不健康行为的增加。但这个结论饱受争议,对左派而言尤其如此。一些人声称这个结论把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本身,因它暗示着穷人和生活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地方的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部分责任,这是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不认为指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健康的确受到吸烟、酗酒、暴饮暴食和缺乏锻炼等因素的影响——就能确定过失方。只有当你假定这些行为全都是由于不幸的懦弱性格造成的时候,受害者才应受到指责。然而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生活在贫困和不平等的环境中,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也被扔到这样的环境中,也有可能以更加不健康的方式生活。
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2015)的一篇论文揭示了一个惊人的趋势,不平等和不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论文中提到的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等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都在稳步下降,然而作者却注意到了一个显著的例外: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上升了。 [7] 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没有念过大学的白人男性群体之中。美国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也比较高,但是比先前有下降趋势,其他少数族裔也是如此。
这一群体受到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们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并不高,却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杀、慢性病以及麻醉剂和止痛药的过度使用。
这种趋势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它涉及了主观上的社会攀比。这类人群死于和自我期望的背离。尽管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平均收入比同等教育程度的黑人高,但出于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凯斯和迪顿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固化意味着这一代人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代财富不及父辈的人。
觉得自己落后的人群的不健康行为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平等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但是也仅仅是部分解释而已。目前最好的统计表明,不健康行为在不平等和健康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中约占三分之一的权重,剩下的大部分权重来自人体本身应对危机时的机能。正如在面对危机时,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会优先考虑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套复杂的机制以采取相同的策略,这套危机管理系统是为了保护“现在的你”而特别设计的,即使这样的设计也许会缩短你的寿命。
这套危机管理系统被称为“压力/应激反应机制”。压力是人体最原始的“发薪日贷款”,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中,对压力的察觉是相当晚的,在人们意识到它的影响之前,它就被平静地慢慢消化掉了。汉斯·谢耶(János Hugo Bruno“Hans”Selye)是一位匈牙利内分泌学家, [8] 20世纪30年代,这位年轻学者曾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在那时,他的研究包括将老鼠卵巢中提取的化学成分注射到老鼠体内,以此评估这些化学成分对动物身体的影响,希望能识别出一种新型激素。
最初实验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注射卵巢提取液的老鼠出现了一些特定腺体的增生,同时其他腺体萎缩并出现了胃溃疡。这些情况的出现,像极了一种新的激素反应。谢耶随后检验了对照组的老鼠,这些老鼠被注射了另一种不同的激素提取物。令人困惑的是,老鼠们表现出了同样的症状。因此,他又测试了另一种提取物,接着又换一种。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之后,他发现:无论给老鼠注射什么似乎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谢耶的目的并非为了发现一些不知名激素的独特效应,他的困惑在于这些现象到底是针对什么东西的压力反应。这些压力反应到底是来自注射入它们体内的物质?还是只是扎针的刺激?谢耶做了更多的研究,希望精确识别究竟哪种创伤会产生这些症状。他的研究包括一些十分残忍的内容,现如今是绝不可能被研究伦理委员会通过的——他向老鼠体内注射了吗啡和甲醛等化学物质;他切除了老鼠的皮肤,破坏了老鼠的骨骼;他把老鼠冷冻起来,也把一些老鼠饿上好几天。
谢耶追踪了每一个实验,他解剖了这些实验对象,仔细观察老鼠在每种特定的实验处理下的身体反应。他最终发现,每一种残酷的实验处理都让老鼠产生了实质上相同的生物应激模式。
这个实验结果让谢耶回想起了很多年前,当自己还是一个医科学生时便关注到的一些事情。他的导师让学生观察五个受到不同疾病困扰的病人。这个练习的初衷是让学生注意每种疾病有着特定的症状,譬如麻疹产生的小红点和流感引起的小红点是不一样的。但是谢耶认为,最显著的问题是所有病人的许多症状是共性的,例如发热、没有食欲、周身疼痛和扁桃体肿大等。当谢耶指出,也许有一种“只要生病就会产生的综合征”存在的时候,教授不以为然,这个提法也就不了了之。然而,谢耶在老鼠身上发现了这种不管采用怎样的处置方式都会表现出共同症状的现象。
谢耶一开始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一般性适应征候群”,后来简称为“应激”。生理学家不太能接受这个观点,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特定化学物质和特定身体反应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体是一种类似于瑞士军刀的存在,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解决每项任务,或者是一种锁钥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细分的钥匙分别打开对应的各种复杂的锁。然而,谢耶认为人体事实上比以上对应要混乱得多。以任意方式干扰这个系统,你会得到相同的通用应激。他的指导教授称之为“垃圾药理学”。
谢耶的结论在细节上存在很多错误。例如,他认为长期压力是有害的,因为当人体耗尽了压力激素时并不能得到足够迅速的补充。一旦激素耗尽,人体便会处于无防备状态。随后,一些证据显示他受到了烟草公司的大力资助,这让他的研究动机受到质疑。这些烟草公司利用他的研究做诡辩:“烟草不危险,压力才危险,人们只是通过吸烟缓解压力而已。”
然而,作为“应对任何危机而产生的一般身体反应”的压力概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我们理解的压力反应是指机体为了应对威胁和机遇而准备消耗大量能量的方式。
为了理解压力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正在大草原上觅食的采集狩猎者。忽然间,在你身后的高草丛中传来一阵窸窣声,草丛后可能是一头狮子,也可能是一名敌对部落的勇士,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你都处于危机之中,或战或逃。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一只野兔,若如此,你就得抓紧行动解决今天的晚饭问题;也有可能是一头野猪,勉强能算一顿“潜在的晚餐”,因为若你不能迅速精准地搞定它的獠牙,那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你没有太多时间判断这声音究竟意味着危险还是机遇,或者两者都有。你的全部机体在远小于一秒的时间里就会被调动起来重新定向,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惊喜或者惊吓。
你的大脑指挥各种腺体通过复杂的链式反应将激素释放到血液中,进而引起细胞变化。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是两种最重要的压力激素,它们和其他激素一起将细胞中储存的来自食物的葡萄糖、蛋白质和脂肪解锁,并释放到血液中,为肌肉提供能量。他们也会干扰胰岛素,而胰岛素的作用正是将血液中的葡萄糖转移到细胞中储存,以备后续使用。
当大量能量供给涌入血液时,就需要开启循环系统,使每种能量被快速地运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压力激素提升心肺系统,为血液流动提供更多的氧气,同时引发血管收缩,使每一次心跳泵血都更加强有力。血液的流动就像水流经一个部分褶皱的软管那样,通过半径的减小会在霎时间造成血压的提升,把涓流变成涌流。心脏病也多发于这种压力时刻,因为这正是心脏活动最艰难的时刻。
在潜在危机面前,人的身体还有另一个重要资源,那就是水。压力激素示意肾脏停止从血液中吸收水分以制造尿液,同时,全身的水分将从各个组织中转移到血液里,以便按需使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在婚礼上致祝酒词的时候会感到口干,因为此刻你不会希望自己的舌头粘住口腔上颚。
最后,你的压力系统引发了一种免疫反应——炎症。我们通常经历的炎症是创口,或者是一个蚊虫叮咬的红包,它让你感到痛,或者形成溃疡,或者造成嗓子的刺痛。它会让你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疲劳,而是得了感冒。人体将免疫细胞释放到潜在感染的组织中,准备杀灭入侵的有机体。我们受到感染时体会到的痛苦,正是人体对抗感染的反应。这是人体自身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混合体。
这场歼灭战中的主角之一是巨噬细胞,这种被翻译成“大胃王”的细胞不像免疫系统的其他部分那样,可以记住特定的入侵者,然后锁定并摧毁它们。炎症进行攻击的策略有点像是地毯式轰炸,这些细胞遇到异己时只会问一个问题:“这是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自身的分子标记未被检测出来),那么巨噬细胞就会将其吞下。
我们通常认为,免疫系统是被动反应的。只有在细菌和病毒侵入体内时,免疫系统才会发动自卫反击。这一点没错,但是我们的压力反应并不会等到我们的身体边界被真正入侵时才开始启动。一有风吹草动,机体就会争先恐后地发起措施先发制人。炎症细胞这时就会偷偷潜入血液中,做好防御准备。
这种优秀的危机响应系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的身体有能力让我们保持精力充沛,并部署一块先发制人的免疫防御盾供我们快速应对挑战,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压力条件下,才会启用这一重要能力呢?为什么不能在每时每刻都开启这种能力呢?
第一个原因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这一点上,进化过程与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压力并不创造能量,只是改变了能量的方向。当压力反应在一些方面提升了机体能量时,它必须从其他地方再取走这些能量。在面对潜在的紧急情况时,你的身体就会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功能。在这时,涌入血液中的葡萄糖和蛋白质暂时不会用于细胞分裂、细胞维持、细胞修复或传递给肌肉这类长期的生命活动。
例如,作为一项长期生命活动,消化在这时就会戛然而止。因为如果你活不过接下来的几分钟,那么消化这种功能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样,生长进程也会停止,从而引发“压力侏儒症”。长期经受巨大压力的孩子——受到虐待或是无人照看——即使他们营养充足,其生长也可能受到阻碍。
让我们不能总是享受压力“福利”的第二个理由是,它会引发可怕的副作用。我们通常认为身体的反应是自然发生的,对我们自身无害。但是在压力下产生的激素,本质上是人自身生产的强力药物。医生使用可的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合成物)和其他压力激素作为药物应对一系列问题。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药物必须少量使用,因为它们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像其他药物一样,我们自身产生的压力激素只有在偶尔和短期使用的条件下才是安全的。但这并不是我们通常使用它们的方式。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压力研究专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认为,如果我们像其他动物那样利用自身的压力反应,那么我们在收获福利的同时,就能够避免许多损失。正是这种非凡的特质使得压力成为整个动物王国中最杰出的力量推进器,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人类的痛苦和疾病。正如我们所知,压力的卓越能力正在于它不需要等到真正的组织损伤才发挥作用,而是当面临潜在威胁时便会触发。然而,人类可以感受到那些此刻并非实际发生的威胁。如果让你只花几分钟去想想那些令你害怕或者焦虑的事情,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心跳加速,体温上升,说不定还开始流汗了。这说明仅仅运用思维便可触发压力反应。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可以夜不能寐,因为担忧着明天的PPT演示,下个月的按揭付款,或者背后那颗奇怪的痣。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还在于,我们可以一次性地将压力反应开启数周、数月甚至数年。考虑到它的衍生影响,我们正在开发设计一套为了重新定向各种资源,避免其在短期紧急情况下耗尽的系统。这套系统的设计是忽略长期成本的,但其目的则是更好地为长期生命活动所用。
当压力激素长期阻止胰岛素储存葡萄糖时,我们患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就会变得很高。当压力激素导致连续多月的心脏泵血困难和血管收缩时,我们就有可能患心血管疾病。当炎症的发作变得难以节制时,免疫系统就会变得过分活跃,也就开始疯狂攻击所有细胞,不再区分这些细胞是我非我。当免疫系统开始对自身细胞发动进攻时,便会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
压力激素过度刺激的另一种方式便是无法区分有害的入侵者(细菌和病毒)和有害物质(像花粉、尘螨或者食物中的特定成分),这时便会引发过敏。长期炎症也是引发心脏病、抑郁症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风险因素。
这些看来都不适用于现代生活,是不是?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我们对食物和性等事物的渴望可能让自己陷入麻烦,因为在过去几千年里行之有效的东西并不能全部适用于现代环境。这种不匹配体现在“压力”方面。回想我们祖先的生活,他们作为采集狩猎者经历的时光,可比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要漫长得多。考古学家的统计表明,在史前,有15%的人口死于暴力, [9] 这比包含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其他种族屠杀在内的20世纪的所有死亡总数的5倍还多。在现代卫生条件和抗生素出现之前,轻微感染便会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在古希腊,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面对如此之多的暴力与疾病,又没有现代医疗手段,压力的自我治疗是我们应对来自传染病和受伤等严重威胁的最佳帮手。如今,我们自身威胁响应体系的武器库依然强大如初,但威胁本身发生了变化。
像我们一样,我们的祖先也会躺在洞穴中夜不能寐,为明天而担忧。但对他们来说,压力的积极作用远大于其消极作用。但我们比祖先幸运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活得足够久,久到死亡通常发生于年迈时被疾病压垮,而不是被草丛里的捕食者吃掉。然而,这种幸运也是有代价的,其代价便是:在现代环境中,压力的副作用带给我们的危害,远比压力进化到能够防止我们所受威胁的危害要大得多。如今,在经济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死因便是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这些疾病都可能是由压力引起的,或者因压力而加重。既然现在没有什么生物能杀死人类,那么这种压力治疗机制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加可怕。
由于压力是身体为应对眼前威胁而采取的一种集中应急方式,其代价便是牺牲身体的长期活动。那么,困难的经济境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会引发机体的压力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各种研究已经证实了压力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例如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对肯尼亚国家公园中的野生狒狒的研究。 [10] 萨波尔斯基花了很多个夏天观察这些狒狒,逐渐熟悉其族群中的个体成员和它们各自在族群中的地位。为了衡量它们的压力程度,他用药用飞镖麻醉狒狒,然后提取了它们的血样。萨波尔斯基发现,在族群中地位越低的狒狒,其压力激素水平越高,也越容易患一些包括溃疡在内的压力相关疾病。但是那些地位较高的雄性狒狒可以任意选择雌性交配对象,随意攻击那些地位较低的其他雄性,因此它们的压力等级很低。
有一年夏天,萨波尔斯基发现狒狒群开始在一个旅馆旁边的垃圾坑里觅食,这对于它们来讲简直就是在享受自助餐盛宴。当然,不是所有狒狒都有资格奔赴这场盛宴的,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狒狒才可以享用这些战利品。垃圾食品的摄入导致它们发胖。但讽刺的是,在这些垃圾堆觅食的狒狒之间,一种牛结核病开始传播,这种疾病在它们的自然觅食地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位于统治地位的雄性狒狒相继死去,而族群的等级制度依然如故,只不过那些原本最具侵略性的雄性狒狒不再是族群的统治者了。这时,萨波尔斯基再次对原本属于下层的雄性狒狒进行血样分析。他发现,在这个重新形成的扁平等级社会中,这些下层雄性狒狒的压力激素水平下降了。
关于狒狒群的实验室研究表明了族群中的“高地位”与自身的“低压力”之间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能解释,究竟是“低地位”引发了“高压力”,还是“高压力”导致了“低地位”。也许这些焦虑的狒狒正是被族群中有低压力倾向的成员所统治。因此,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实验性地改变一群生活在实验室中的猴群的等级关系。 [11] 首先,他们证实了在初始的等级制度中,个体的社会层级越低,它的压力激素水平就越高。随后,研究人员帮了“低地位”的猴子一个大忙,他们把猴群中的统治者永久性地带走了。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你将最顶层的统治者带走,那么“中层干部”的压力激素水平便会下降,因为它们发现领导的缺失会带来其自身地位的瞬间提升。实验室实验解决了萨波尔斯基在野外研究中产生的疑惑,是等级排序的不同引起了压力水平的不同,反之则不成立。
提升压力反应在地位较低的灵长类动物中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因为最容易遭到殴打撕咬,也最容易被夺走食物的正是这些地位较低的个体。相对于那些地位较高的雄性,这些地位低的灵长类个体需要更加频繁地调动其身体资源应对突发状况。人类是否也如此呢?我们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却有许多与灵长类动物相同的分级结构。只不过动物的分级结构是以食物和交配权来衡量的,而人类的分级是用金钱、权利、社会地位和社会比较来衡量的。基于对动物的研究,可以设想,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应该会比其他人承受更大的压力。
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压力激素水平,其血液中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也更高。反应过度的免疫系统和更高的炎症水平更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现。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交易员这一人群的压力水平和炎症状况,发现在这一人群中处境更贫困或是自我感觉地位较低的个体,其压力和炎症水平都会相对稍高。然而,当你将这些个体暴露在压力下,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反应的,你就会发现巨大的差异。
一项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鲁·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发起的研究招募了在英国公务员系统中任高职位和低职位的志愿者。 [12] 安德鲁给他们安排了需要完成的压力任务。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需要用一支笔追踪在电脑屏幕上移动的星星。这听起来很容易,然而志愿者却只被允许通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手,所以出现在右边的星星实际上是在左边,反之亦然。在实验设计上,星星的移动速度非常快,会导致实验对象出现错误。一旦实验对象的笔迹偏离了星星的实际移动路线,电脑便会哔哔作响。为了确保实验的压力,实验人员告诉实验对象,他们的“平均水平”可以精确追踪到星星的轨迹,这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错误会让实验对象觉得自己低于平均水平。
在星星追踪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及任务完成之后,实验人员都对实验对象的心率和其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进行了测量。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人群在同样的压力下完成任务,而地位低的人群血液中发现了更多的炎症标志物。而且,尽管两组人群在实验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心率加速,但是地位高的人群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地位低的人群在两小时后依然表现出心率过快的症状。
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心理学家基尔·慕斯凯特尔(Keely Muscatell)和她的同事利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获得了相似的结论, [13] 给这一理论添加了一条令人信服的佐证。在这项研究中,志愿者面试的情况被录了下来。设想一下你自己是志愿者之一的情形:你走进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一间实验室,然后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中涉及你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信息。随后,一位亲切而又专业的大学生与你面谈,问了一些“你生活中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你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等诸如此类的个人问题。
第二天,你又来到了一个实验室,护士在你的胳膊上扎了一针,抽取了你的血样,然后让你平躺在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前,接受脑部扫描。这台设备看起来就像是医院里的病床,不同的是你需要将脑袋伸到一个甜甜圈状的白色结构中。它由光面塑料制成,就是同飞机上座位上方的行李仓一样的材料,跟大众汽车的大小差不多。当一切就位后,你抬头便会看到“甜甜圈”的洞中有一块小型电脑屏幕,这时你才得知另一位实验对象将会观看你的访谈录像,并对你做出评价,而且你将会观看他对你的评价。此时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方形网格,在每一个方格中有一段性格描述。当其他实验对象观看你的访谈视频时,他会在屏幕上移动光标,通过点击方格对你进行赞扬或者批评。前一分钟她认为你很聪明,于是就点击“聪明”;下一分钟她又觉得你很讨厌,于是就点击“讨厌”。简直太简单粗暴了!又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了“真正的你”,于是再点击“体贴”。这个测试需要进行一段时间,但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并不存在,是实验人员用自己的鼠标在对你进行系统自动的表扬和批评,同时通过你的情绪起落扫描你的大脑,监控你的血流情况。
研究人员发现,当志愿者被“另一间屋子中的人”打量评价时,他们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就会显著提升。这个效应在那些自我评价处于社会地位阶梯较底端的人群中尤为明显,他们的炎症水平飙升。
这些研究中有几点发现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我们通过实验证实了社会地位评价的确会引起炎症水平的改变,而不仅仅是笼统地说这两者之间有相关性;第二,整个实验进程大概有90分钟,而炎症水平的变化在不到一小时中就能被检测出来。人类社会的等级划分无处不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对身体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胞产生影响。
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主观地位评价引发血液中炎症水平变化的途径是由前额叶中特定网络区域的大脑活动控制的。当人们出现一些想法、感受和对他人的看法时,对比大脑的其他部分,这片区域就显得十分活跃。尽管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证实并解释这个发现,但作者认为大脑会积极计算我们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位置,这一做法与我们通常用来获取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的神经机制是相同的。就像萨波尔斯基的狒狒一样,在这个实验中,人们对待低等级排位就像对待真正的物理威胁一样,他人的怠慢如同文字攻击一样实在,使人的身体调动免疫反应。
对于公关公司、紧急医疗救援者或者生物体而言,管理危机的唯一途径便是:优先解决眼前需求,将来的事情先放一边。当然存在一些生物选择了其他方法,但是在危急情况下忽略最迫切需求的个体,也许再也不会有机会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存智慧。当你的大脑向你的血流中倾倒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时,它已经选择了牺牲未来,满足眼下——释放能量,引发炎症反应,为你做好战斗准备。即使有一天这种应激反应会导致你得糖尿病和心脏病,那也无所谓。这就是你的大脑在你全神贯注于灌木丛中的沙沙声,而忽略未来的一切时做出的反应。此时你会忘掉一切,你全身的细胞都会把未来放到一边,先拿到眼下需要的东西。不平等加剧了这个进程,因为它让每个人更加缺乏安全感。我们到底是通过纯死亡率数据还是墓碑上褪色的花岗岩来统计衡量这种效应,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最终都要为危机管理付出代价,似乎未来变成了现在,远景来到了眼前。
[1] G.D.Smith,D.Carroll,S.Rankin,and D.Rowan,“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Evidence from Glasgow Graveyard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5(1992):1554-57.
[2] T.Jackson,“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The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Econom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2009,www.sd-commission.org.uk/data/files/publications/prosperity_without_growth_report.pdf.
[3] M.Marmot,Status Syndrome:How Social Standing Directly Affects Your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London:Bloomsbury,2004).
[4] A.Conan Doyle,“Silver Blaze,”Strand Magazine,1892.
[5] A.Singh-Manoux,N.E.Adler,and M.G.Marmot,“Subjective Social Status: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asures of Ill-Health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Social Science&Medicine 56(2003):1321-33.
[6] R.Wilkinson and K.Pickett,The Spirit Level: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New York:Bloomsbury,2010).
[7] A.Case and A.Deaton,“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2015):15078-83.
[8] H.Selye,The Stress ofMy Life:A Scientist's Memoirs(New York/Toronto:Van Nostrand Reinhold,1979);G.Gabriel,“Hans Selye:The Discovery of Stress,”April 5,2013,http://brainconnection.brainhq.com/2013/04/05/hans-selye-the-discovery-ofstress/.For an accessible discussion of the stress response in humans,see R.M.Sapolsky,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New York:Henry Holt,2004,third edition).
[9] L.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0] R.M.Sapolsky,A Primate's Memoir:A Neuroscientist's Unconventional Life Among the Baboon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7).
[11] R.C.Stavisky,M.R.Adams,S.L.Watson,and J.R.Kaplan,“Dominance,Cortisol,and Behavior in Small Groups of Female Cynomolgus Monkeys(Macacafascicularis),”Hormones and Behavior 39(2001):232-38.
[12] A.Steptoe,N.Owen,S.Kunz-Ebrecht,and V.Mohamed-Ali,“Inflammatory Cytokines,Socioeconomic Status,and Acute Stress Responsivity,”Brain,Behavior,and Immunity 16(2002):774-84.
[13] K.A.Muscatell et al.,“Neural Mechanisms Linking Social Statu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to Social Stress,”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2016):915-22.
如果你手上有28000美元,你会怎么花?买辆新车?付一栋房子的首付?还是还上你的助学贷款?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的戴安·迪瑟(Diane Duyser)选择把自己的28000美元花在烤芝士三明治上 [1] ——这可不是普通的三明治,而是能看见圣母玛利亚头像的三明治。这件事证明,此类奇葩到处都是——俄罗斯的村民崇拜桦树皮上的耶稣像; [2] 一个威尔士家庭在一块瓶盖上沾着的马麦酱渍上看到了基督; [3] 而一个纽约人则在他的脐橙上发现了主。 [4] 近些年来,“神圣家族”曾在奇多、椒盐脆饼干、洋葱圈和早餐玉米卷上显灵。 [5] 这个早餐玉米卷的售价也高达600美元。
这个偶然看到偶像形象的癖好被称作“空想性错视”。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就注意到,在人类中存在一个“凭借那些他们能轻松习得的能力,把众生都想象成自我和变成任何事物的普遍趋势……他们在月亮上能看到人脸,在云彩上能看到军队;而且,通过一种本能的偏好就把邪恶或美好的祝愿归咎于一切,而它却不被实验和深思熟虑所修正,这也许会伤害我们,也许会取悦我们。” [6]
人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在零食上看到神灵的“普遍倾向”呢?正如我们将要知晓的那样,这些形象与曾经经历过这些形象的人的大脑的关联程度,远比其同精神世界的关联更大。但是这些人并不是脑袋坏掉了。相反,他们正在从事一项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的活动,这项活动将秩序和理性带回我们的生活之中。随机性和混乱让人感到威胁,但是有秩序的模型使我们安心,让我们感到这世界是可预测的、值得信赖的和可控的。当人们在混乱中探测模型时,他们是在从一个明线太少、灰色地带又太多的世界中提炼意义。当然,我们并不是随便一种模型都看的。面孔的模型尤其常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面孔的信息量尤其大,宗教偶像的面孔则更具有唤起人情感的作用。当一种意义感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史诗般的崇高感——古希腊人仰望星空,看见的是神灵和英雄们的星座,而不是跑腿儿小哥。

图6.1 你在这片云上看到一张面孔的容易程度,取决于你在此时的需要
资料来源:Wanda Hartwigsen/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Commerce。
通常认为,我们对于周围事物的感觉是单纯地被事物本身驱使的。而且,我们总是想当然地假设,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是被世界本身驱使的。但不管是我们的感觉还是信仰,它们同样也是被每时每刻存在着的需求和欲望所驱使的。譬如,我们饿肚子的时候会觉得食物格外美味;当我们觉得寒冷时,温暖让我们感觉更舒服;而当我们急切需要一个解释的时候,一些故事看上去就更真实了。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索不平等在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真实”的感知,包括宗教体验和我们所珍视的信仰。我们都想生活在一个稳定可预测的世界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可控的,混乱也是可控的。我们也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在那里,好人有好报,坏人遭天谴。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试图整理这个世界。但不平等穿着泥泞的鞋子闯进门,唤醒了门内的无序和混乱。
理解此事的关键:人类的大脑正是一种模式探测器。举例来说,视觉系统接受了一个持续变换光色与动能的弹幕,并试图从中建造一个稳定的三维世界影像。在这项工作中,大脑是相当有效的,比如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不知要领先多少光年。这不是因为人类的眼睛是非常精确校准的传感器(数码相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清楚),而是由于大脑在查找、逻辑跳跃和基于假设填补空白等方面的表现更加优秀。
你之所以能够捕捉到大脑在填补这些空白时的过程,是因为人类的眼睛有一种设计的癖好,这种癖好能够创造出一个视觉上的大工程。视网膜是一层覆盖在眼球背面的视觉感光器,它将光转换为神经信号。这些信号被视神经所负载,穿过眼球的背面到达大脑。但是视神经离开眼球的位置会留下一小块没有视觉感光器的光斑,因此每只眼睛都会有一块盲区。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个小瑕疵,因为大脑从一只眼睛中获取的图像,会“填进”我们“应该”从另一只眼睛中看到的东西。只要有一只眼睛能看到另一只眼睛遗漏的部分,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洞”。
你可能曾经见过下面这张被用来解释这个盲点的存在的图?但我想用它来说明大脑是如何填满感知空白的。首先蒙上你的左眼,然后用右眼盯住这个十字。把书页从你的面前由近及远地缓慢移动,同时始终盯紧这个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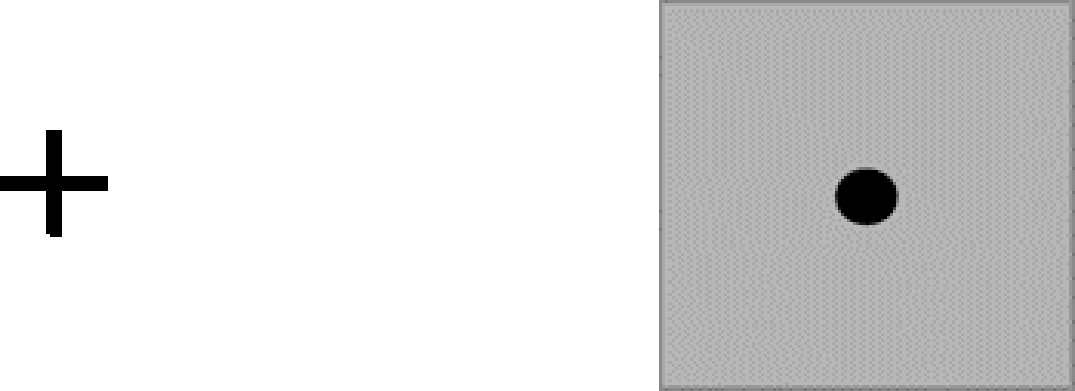
图6.2 你的视觉系统通过使用从环境中得出的假设来填补盲点
你应该会注意到两个东西。首先,在一个特定的距离,这个点会消失,暴露出你的盲区。因为你已经蒙上了左眼,这就不再能提供通常被用来填补这个图像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你会注意到,当这个点消失的时候,这个盒子就会立即被灰色填满。尽管你的左眼不能向右眼泄露关于这个点的消息,部分右眼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灰色的盒子。因此,大脑就会尽可能地用大部分相同的颜色来覆盖整个盒子。
现在你可以换眼睛了。这次蒙上你的右眼,盯着这个点。这一次,当十字消失时,空间被白色所填满。即便是作为一个感知明暗的基础行为,大脑还是做出假设去填补了这个空白。大脑假设这个世界并不是随机的;即便只掌握了部分信息,它也能确定地猜出遗漏了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所在。
关于这个世界是有序并可预测的假设是一种心理基石,形成了我们所有的感知、思考和信念的基础。我们十分擅长生产规范的模型,使其能够在根本没有模型存在的时候干预我们的认知能力。试想一下你在买一张彩票,需要选择六个数字。以下哪一种数字组合更有可能被随机抓取到?是1 2 3 45 6,还是43 7 17 38 9 24?答案是这两组数被抓取到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即便它们看上去被抓取的可能性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第一组数中识别出一个模型,而模型看起来就是与随机性相反的存在。
网络上充斥着关于如何成功选中彩票数字的讨论。 [7] 中奖七次的理查德·卢斯蒂格(Richard Lustig)推荐票迷们自己选择数字,而不是依赖自动的“快选”数字。 [8] 网络评论家同样推荐使用对个人来说有意义的日期,同时也有人严肃地提醒反对这种做法。有人建议“使用一个彩票数字产生器会增加你中彩票的概率,因为它选出数字完全是随机的,就像彩票机器一样。”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误读了随机性的本质。随机的定义是:任何数字都有同样的出现机会。跟这组数字产生于你自己,还是一部机器,或者是你最喜欢的叔叔都没有关系;其排列跟是不是像你第一个手机号那样随意,或是像你母亲的忌日那样神圣都没有关系。随机性意味着没有原因,也没有效果。在你如何选取数字和到底产生了什么数字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它没有模型,也没有顺序。除了指示谁是赢家之外,这些数字全然被抹去了意义。
如果我刚刚所说的彩票数字毫无意义的事实让你感到泄气,那么你就能开始认识到模型和我们寻找意义的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有多近了。模型是令人舒适的,甚至在主题是完全随机的数值计算的时候,坚持认为没有潜在的秩序或者更大的意义会让人感觉有点像是欺负人。
就像休谟声称的那样,在偶然中发现有意义的模型的倾向是普遍的,但是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机会比其他场合更多。当我们感到无力的时候,我们就尤其喜欢去生产有意义的模型。这种对于模型的预测为我们从控制的缺失中提供了一点安慰,因而也是一种控制力。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开着沃尔沃的会计看上去永远不会在他的肉桂吐司上看见耶稣。
心理学家珍妮弗·惠特森(Jennifer Whitson)和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在一系列实验中直接检测了无力感和空想视错觉之间的关系。 [9] 在一个场景中,研究人员通过要求实验对象非常详尽地讲述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使其再体验一遍那种完全失去控制的感觉,从而使得实验对象暂时感到无力。另一组实验对象则需要讲述一次他们觉得事情完全在控制之中的经历。接着,实验对象观看了一组随机的黑白“静态”照片,然后被告知其中一些形象中包含了一张隐藏的照片,并被要求认出这些形象是什么。事实上,这些形象纯粹是干扰项,但是“无力的”实验对象差不多有三倍的可能性看出在这个静态中隐藏的照片。这种转瞬即逝的无力感使他们的大脑更努力地从无意义中提取意义。
心理学家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与其同事的一项调查发现,当人们感到自己被遗漏 [10] 、被落下或是在社交上被隔离的时候,他们同样也有可能开始把自己身边的事物人格化。这时,他们的狗和猫看起来就跟人类很相似了。上帝、幽灵和恶魔看起来像是实体。就算是闹钟这种无生命的物体,你都会认为它是一个有知觉的存在——这个闹钟其实是故意在大吵大闹。
在云朵、闹钟或者芝士三明治上看到人脸,是一种在混乱中强加秩序的方式,但是它并不是最普遍的方式。一种被我们用来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更典型的手段,是编造我们周围世界的故事。那些让一切看上去都能与我们的理解契合的手段是最有效的,但是其中一些最能满足条件的手段有着难以想象的性质,让你很难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最近,一个民意调查人询问了1200多个美国人在不同议题上的意见。 [11] 有28%的人相信,有一个神秘的、带着全球主义日程表的权力精英,正在密谋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来统治世界。这个“新世界秩序”是一种与光明会(一个声称要主宰像共济会、好莱坞电影工业和美国政府等组织的秘密社团)有关的阴谋论。在一些叙述中,这个组织也被称为SPECTRE(幽灵党),是詹姆士·邦德系列书和电影中的超级反派联盟。28%的人啊!如果按这个百分比推到全部美国人口,相信这个阴谋论的美国人的数量就是8800万!
这个测验还发现,21%的回应者认为一个外星UFO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坠毁了,而且政府掩盖了这一事件;51%的人认为刺杀约翰·肯尼迪是一场阴谋,而不是一个孤枪侠的作品;37%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15%的人认为制药工业与医疗公司是穿一条裤子的,它们为了赚钱而发明新的疾病;4%的美国人(差不多1200万)相信“能在人和爬虫之间变形的生物,会通过变成人形获取政治权力,从而掌控社会”。
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某种形式的阴谋论, [12] 而且这个比例已经维持了好几十年。这些理论有着特定的形式。饱含愤怒的阴谋论经常会广泛流传,最终不可避免地被遗忘。美国内战期间,在北方广泛流传着一个阴谋论:“奴隶力量”——一个由蓄奴州的权力人士组成的秘密联盟,一直在秘密刺杀联邦政府官员。
实际上,阴谋论跟两件事情有关:权力和不信任。你可以在相信关于某人的阴谋论的著作中看到权力。对人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相信哪个阴谋论最好的预测器就是看看哪个政党正在执政。我还在上述民意测验中发现,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相信,由小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纵容了“9·11”恐怖袭击的发生。而在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下,各种阴谋层出不穷,说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还是个秘密的穆斯林等。这些阴谋论主要被右派人士所相信。感到无力的人们倾向于相信由权力人士提出的阴谋论。
惠特森和加林斯基用与他们在研究权力和空想视幻觉的关系时使用的方法,调查了在权力和阴谋论之间的关系。他们设计了一个使一组实验对象感到无力,而另一组实验对象感到有权力的实验。然后,他们给两组实验对象展示了一些对每天发生的事件类似偏执狂的、基于阴谋论的解释,并询问他们这些解释的可信度有多少。感觉无力的组员比感觉有力的组员觉得阴谋论的解释更可信。这个实验为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原因建立了一些“原因—效用”的第一手证据。感觉无力的人们并不只是由于一些像智力、教育水平或者个人喜好等个人特质才碰巧更相信这种理论。相反,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才是主要动因。
由心理学家迈克尔·伍德(Micheal Wood)和同事进行的一个研究检验了奥巴马治下的两个关于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死的阴谋论。第一个阴谋论说美国的海豹突击六队并没有真把本·拉登杀死,他其实早在军队袭击其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住宅前就死了;这个袭击仅仅是为了让奥巴马总统能得到杀死了恐怖主义头子的好名声而组织的罢了。第二个阴谋论说本·拉登不仅没有被杀掉,而且现在还活着,他正秘密地操控着基地组织,策划着新的恐怖袭击。
伍德发现,坚信第一个阴谋论的人同样也更有可能相信第二个阴谋论,即便从逻辑上讲,本·拉登几乎没可能在公认杀死他的袭击之前死掉,或是到今天还活着。研究者发现,相信这两个阴谋论的共同元素是对于当局的不信任:那些认为当权者很可能掩盖事情真相以欺骗公众的人更有可能接受这两个阴谋论。不信任——与事实和逻辑都无关——使得即便是自相矛盾的阴谋论看上去也比官方报告要真实。要相信一个阴谋论,你需要让渡一些观念——譬如世界是美好的、公平的和正义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至少存在一些人,或者说总会有人,能把所有事情尽在掌握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对公正世界的信念。人们对世界维持着这种有序感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仅仅是坚信它确实是有序的,然后把所有事情加总起来,回填他们的推理过程。许多年前,心理学家梅尔·勒纳(Mel Lerner)通过组织一个精心安排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 [13] 在一间实验室里,一个连接着电线和电极的年轻女人坐在桌前。她正在接受一项学习和记忆的实验,从实验者处收听问题并给出回答。一旦她犯错——她犯了很多错误——实验者就对她实施电击。这个场景是戏剧性的:她大叫,她哭泣,然而实验无情地持续下去,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
在现实中,这个年轻女人是一个演员,她接受的是假的电击。这项实验中的真正主体在这面单向透光镜的另一面,观察这个经过科学净化的折磨的展开。他们被要求观察这个“学习者”,并给她在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的实验中表现出的情感评级。在10分钟的电击过后,一组参与者被告知实验会一直持续,中间没有休息。另一组参与者被告知电击会暂停,在休息过后,这个年轻女人会因其忍受的痛苦而得到现金补偿。事后,研究者要求实验对象给他们对这个年轻女人的印象评分。事实上,从头至尾,研究者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印象”。
对于相信这个女人将为她所承受的痛苦得到补偿的那个组来说,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万物之逆旅”而已。的确,她在电击中受到了折磨,但是报酬也足以抵扣这种折磨了。但是,对觉得这种无意义的折磨还会继续的那组来说,这个处境看上去就相当荒谬且不公正了。这个可怜的被试为了一个愚蠢的实验而忍受痛苦,而且观察者完全有理由同情这个可怜的人。然而,他们却对她深表遗憾。认为她会继续忍受痛苦的那组人认为她是讨厌的,不成熟的。他们说自己很难去羡慕或是尊敬像她一样的人,因此他们也不会想要去理解她。勒纳预测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为了保持对“世界是公平的”的确定性,实验对象人为地为这个女人的性格制造了一些瑕疵。就像你的视觉系统用假想填充了某个场景,以图把世界呈现为理性的,你的道德推理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好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而坏事情就发生在坏人身上,现在,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因此,她一定是个坏人——完美!
当人们尝试去解释为何一些人挣了很多钱,而其他人却没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思维机制。在勒纳的另一个实验中,他让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猜谜语,让实验对象在单向透光镜的背面观察这个过程。然后,实验者解释道,他的钱只够付一个猜谜者的,于是他从一个礼帽中拿出了一个名字,然后给这个幸运者付了钱,而另一个人就空手而归了。即便这些实验对象刚刚才亲眼看见这个名字是被随机抓取的,但他们却认为这个幸运者工作更努力,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比另一个人更具创造力。对于我们能得到自己应得的这件事情的确定性,以及我们值得获得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的确定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超过了这只是个随机结果的感官证据。
在头脑中扭曲我们通往公正之路的倾向,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受勒纳实验启发,经济学家杰弗瑞·巴特勒(Jeffrey Butler)最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拿到高薪就会让人们觉得自己高出其他人? [14]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让几组实验对象完成了一个关于逻辑推理的实验。在每个组中,有一半的人被告知他们每答对一道题,就会得到4美元,而另一组则被告知,他们只会被付给2美元。就像勒纳实验那样,研究者公开告知实验对象,谁拿到怎样的支付比例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在答完这10道题后,实验对象被要求为自己的推理能力打分。拿到最高金额的实验对象即便并不比其他人在推理实验中表现得更好,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卓越的推理者,也比那些拿到低金额的人更加努力。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拿到低金额的人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怎么优秀的。
在现实世界中,成功和失败是被天赋、努力和机遇等复杂因素的组合驱动的,我们甚至更不愿假设,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对那些在失败一端的人来说,这种假设是与他们的自身利益相背离的,但是它还是为了一个目标服务:这种假设有助于使他们重新确信,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无序的。这个系统也许不是为他们服务的,但起码还是有个系统在的。
大部分人不会停止对“世界是一个公正的所在”的假设的信任。这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掌握在一些公正的人的手中。一神论的宗教为其信仰者提供了这样一个保证:一个仁慈的、全知全能的神正控制着宇宙。这种信仰体系有很多好处。不像以牺牲仁慈为代价而提供可控性的阴谋论,宗教信仰才是真正的双赢。
关注心理学起源和宗教信仰的结果的科学,在观察这些信仰本身是自洽还是自我矛盾等方面同样适用。对于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他们都相信关于上帝的、互斥的事物。解释信仰和非信仰的心理原因,并不能充分说明没有上帝存在;就像解释为什么与非信仰者相比,信仰者得到了确定的情感利益,也不能说明上帝就存在一样。就像伏尔泰所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创造他也是必要的。” [15]
如果感到无力和不安全使得人们更加有可能看到模型, [16] 也更有可能去相信阴谋论,那么它同样也会加强宗教信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阿伦·凯(Aaron Kay)的研究已经证明,当个体感到无助,或是这个世界被描绘成无序或是无法预测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一个强有力的上帝统治宇宙持有更加强烈的信念。信仰者通常用像“让我们跟随上帝”或是“万物事出有因”这类口号来宽慰自己。感到无力放大了这些观念的吸引力。
在另一个研究中,心理学家库尔特·格雷(Kurt Grey)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通过汇编婴儿死亡率、癌症死亡率、传染病、暴力犯罪和环境灾难的数据,观察了美国各州或多或少承受着生活艰难的人们。他们把这些社会问题组合成了一个单一的“苦难指数”, [17] 并根据每个州在民意测验时说自己坚信上帝的人口比例来计算这个指数。许多神学家发现,给宗教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它看起来是矛盾的——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上帝竟然能够允许痛苦的存在。但是这些研究者发现,痛苦并没有为绝大多数信仰者造成神学上的问题。截然相反的是,就像圣经里的约伯那样,人们承受的痛苦越多,他们就越相信上帝。
这个发现支撑了一种观点:当社会更加富有、经济更加发达时,宗教就开始衰落。这个观点几乎被19世纪的大知识分子普遍接受。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涂尔干之间的思想差异大到不能再大了,然而他们都同意,当文艺复兴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进步扎根时,宗教将会消亡,而像进化论这样的科学理论将代替对神创论等理论的信仰。微生物理论将会代替原罪和恶魔附身,成为疾病产生的原因。当现代医学赋予人类控制那些折磨他们千年之久的疾病的能力时,精神治疗师和萨满巫医就会让位于医生。从现代农业到空调,技术会让生活在多变的大自然面前不那么脆弱。在我们理解宇宙运行和自身起源的研究中,宇宙学将会取代神学的位置。而且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共同鼓励对于原因和证据的追寻,当成回答生命的大哉问和解决日常问题的最可靠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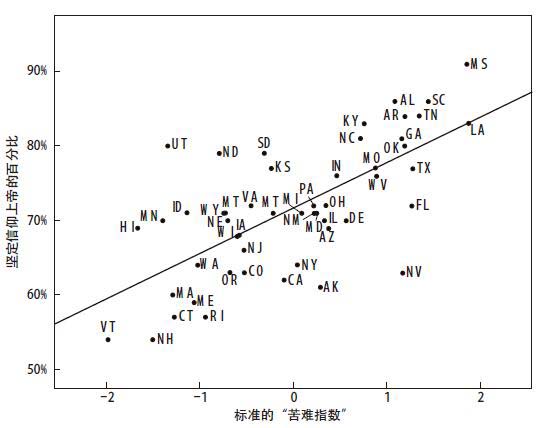
图6.3 人们承受痛苦更多的州对上帝有更加坚定的信仰
注:亚拉巴马AL、阿拉斯加AK、亚利桑那AZ、阿肯色AR、加利福尼亚CA、科罗拉多CO、康涅狄格CT、特拉华DE、佛罗里达FL、佐治亚GA、夏威夷HI、爱达荷ID、伊利诺伊IL、印第安纳IN、艾奥瓦IA、堪萨斯KS、肯塔基KY、路易斯安那LA、缅因ME、马里兰MD、马萨诸塞MA、密歇根MI、明尼苏达MN、密西西比MS、密苏里MO、蒙大拿MT、内布拉斯加NE、内华达NV、新罕布什尔NH、新泽西NJ、新墨西哥NM、纽约NY、北卡罗来纳NC、北达科他ND、俄亥俄OH、俄克拉何马OK、俄勒冈OR、宾夕法尼亚PA、罗得岛RI、南卡罗来纳SC、南达科他SD、田纳西TN、得克萨斯TX、犹他UT、佛蒙特VT、弗吉尼亚VA、华盛顿WA、西弗吉尼亚WV、威斯康星WI、怀俄明WY
资料来源:Gray and Wegner(2010)。
在20世纪中期,这个世俗化理论被当成了一种信条。1968年,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告诉《纽约时报》 [18] ,“到21世纪,宗教信仰者更有可能只组成小教派,他们抱团抵抗世界性的世俗文化……这种信仰者的窘态正在日益增加,就像在一所美国大学中逗留过久的藏族占星家那样囧。”被启蒙赋予力量的人类将不再依赖上帝。
知识分子的预测已经实现了吗?可以说实现了,也可以说没实现。很明显,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清醒,但其从深层意义上还是宗教性的。调查显示,在地球70亿人口中,大约有84%的人拥有宗教信仰。 [19] 虽然对经济和科学发展将如何不均衡地传遍全球的预测失败了,但这个数据或许并不能反映“科学理论终将取代宗教”的论断也失败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地方的日常生活与伯格设想的大学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因此,经济发达国家真的比欠发达国家的宗教化程度更低吗?在这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正如你在图6.4的民意调查数据中看到的那样,国家越富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宗教的重要性就越低。如果我们观察另外的衡量指标——譬如教堂的出席频次或信仰上帝者的比例,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趋势。在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样的赤贫国家,多达90%的人口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富裕国家,只有大约20%的人对宗教有自我认同。这清楚地证明了当人们的生活在物质层面变得更加安全时,他们就不太需要来自宗教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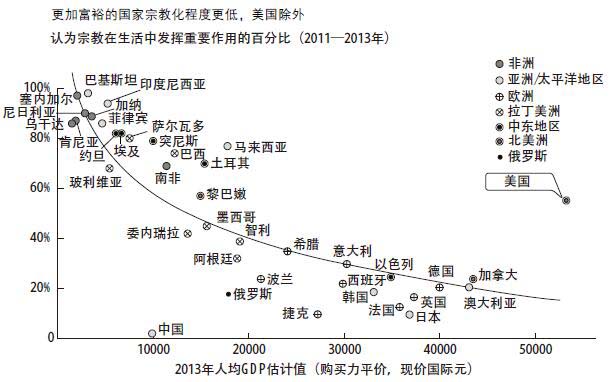
图6.4 更加富裕的国家的宗教化程度更低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然而,这个模型里还是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其中一个很容易解释,另一个则不怎么容易解释了。很容易解释的例外就是中国,在那里,宗教一直以来并不流行,宗教的重要程度远比这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更低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更使人迷惑的例外是高度宗教化的美国。尽管在研究中,美国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而美国的宗教信仰程度却跟墨西哥、黎巴嫩和南非差不多。
当然,除了收入之外,宗教的流行程度还取决于许多原因,譬如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部分程度上是躲避宗教迫害、寻求避难所的移民建立的,这的确是源于其非比寻常的虔诚程度。然而,最近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更加有力的解释。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绍尔特(Frederick Solt)利用可被使用的最广泛的数据库,检测了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等级,可以用来解释总体趋势和例外情况。 [20] 在列出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后,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例外了。但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比更加平等的国家的宗教化程度更高。不平等的作用是巨大的,差不多跟实际收入的影响比肩。一旦这个数据被用于说明在宗教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平均收入),美国也就不再是一个例外了,而且会正好落在它被期望的线上——不平等和宗教化的程度都很高。贫穷和不平等相结合,能够共同解释不同国家在宗教性上的巨大差异。
即便没有研究能够牢固确立不平等和宗教之间相互关联的原因,但我还是可以预测,当这个研究完成时,其关键的一点将会是对于地位和安全的内在感受。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在高度不平等的地方,普通人会觉得自己更穷,地位更低。同样,在本章中我们得知,当人们感到无力或是被遗弃时,他们就更有可能使自己依附于信仰体系,从而使世界看上去更加公平、可预测和有意义。不需要费太多脑筋就能想象出,当不平等程度提升时,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太安全,而宗教看上去就更加有吸引力了。注意到这个趋势与对于某个具体的宗教信仰无关。在基督教主导的国家中,不平等与耶稣信仰的关系更大;在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中,不平等与穆罕默德信仰的关系更大……当人们在世间感到不安全时,他们倾向于投身于任何养育他们的宗教体系。
世俗主义者喜欢指出神圣书中的逻辑不一致之处——神迹不可能发生的本质,以及证明超自然现象的不可能性。但是许多宗教学者已经指出,对于大多数信仰者而言,事实和逻辑根本就不是信仰的基础。宗教并不像科学,是关于一套内在连贯的命题到底是对还是错的集合。相反,许多人是由于其个人主观经验而相信宗教的。这些也许包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惊叹,一个归属于封闭社群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听到上帝以一种熟悉的嗓音跟你说话时的舒适体验。这些感觉都是情感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神学的产物。
穷人不仅比富人更具宗教性,他们的宗教性还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低收入人群更可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语录,与一套普遍的神启教义截然相反。穷人更有可能相信神迹、信仰疗法和恶魔附体。
在肯塔基州长大的我,一直生活在收入低且不平等程度高的环境之中,可以想见,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将会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我所生活的社区是一个充满神迹和谜团的世界。我曾经见到一个虔诚的少女被圣灵击倒——当牧师轻触她的额头时,她变得充满来自圣灵的狂热,她想要做出解释,却立即跌倒在地;另一个女孩抽搐着,好像被连接到一条看不见的高压电线上似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央求一个亲戚给我展示她是如何在宗教仪式中讲那种不为人知的语言的。她解释道,如果你向上帝祈祷,上帝就会把圣灵传送给你,然后你就能像受到神灵驱使一样,自动讲这种语言了。这些语言也许是外星语言,或者是只有天使才能懂的语言。但我亲戚所说的文字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混合体,虽然我曾经希望她说的是更有仙气的语言。
基督教社团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个体层面上体验上帝。在一个美丽的春日,我所在的宗教学校的牧师把我们的课堂移到了室外,去上一堂不平常的课。我们在一片草地上坐下,旁边是一个小花园,黄百合和高草在温和的微风中摇曳。他开始给我们上课,课程基于我们熟悉的圣经诗句:“看看空中的鸟儿: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甚至不用屯粮,是你们仁慈的天父在喂养它们。你们不比鸟儿更珍贵吗?……想象这田野里的百合花,它们是如何生长的:它们既不用辛苦劳作,也不用纺纱,然而我告诉你,甚至是所罗门在他极荣光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闭上眼睛,感受这微风,倾听小草的歌唱,我们就能够听到上帝正通过它们跟我们说话呢。
除了风声和草声之外,我没有感觉到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竖起耳朵去听。风声听起来像是父母轻柔地让他的孩子安静下来。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话,清亮得像风铃:“安宁,请你留下。我将永远照料你。”它像一股电流一般。我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在这一天的学校生活中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其他任何事情上。这天下午,在我乘巴士回家时,我还在脑海中重演这个声音,试图再次捕捉到这个神奇的时刻。
然后,一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听到的那句话其实是我最近学过的两句圣经诗句组合在一起。其中一句是,耶稣要求大海平静下来,而大海遵从了他的命令;另一句是对于“麻雀和百合花”这句诗的解释。我的牧师曾经向我们暗示了一套特定的安慰想法,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引到风声和草声,并要求我们倾听上帝的声音。我如何知道这个声音是上帝的,而不是我自己头脑中想法的表达呢?
因此,我做了一个小实验。我对自己说:“紫色。”然后我闭上眼睛,在满是吵吵闹闹的孩子的车厢里竖起耳朵听这个词。十分肯定的是,我很快就听到了它。是其中一个孩子说了这个词,还是我的大脑从在脑海中飞过的成千个音节中,把这个词凸显了出来?在我用其他几个词继续这个实验之后,我意识到,如果你试图在刺耳的吵闹声中听到什么,那么你就很可能听到它。“特兰西瓦尼亚?”我听到了。“大头菜?”我听到了。也许我这么做是错误的,但是我的头脑看上去就不会再有看到神迹的才能了。
过了几年,我会明白,我在那天经历的一切,是大脑在把圣母的形象做进一个烤芝士中,或是把一打随机发生的事情缝合进一个大阴谋之中。我们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人们觉得他们被落在后面了,生活无序,处境又很不确定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就加快步伐,投入到稳定这个世界的工作中去。而且,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比起不信教的人,信教的人会更快乐,或更少焦虑 [21] ——不管是对生活还是死亡。一些信仰体系以一种普通的思维方式做不到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和信心的恢复。对大多数人来说,学院派神学家所说的那种抽象化的非人格神,则不能提供这种层次上的舒适。生活越艰难,它就会变得越不可思议。
[1] “‘Virgin Mary Grilled Cheese’Sells for$28,000,”Associated Press,November 23,2004,www.nbcnews.com/id/6511148/ns/us_news-weird_news/t/virgin-mary-grilledcheese-sells/#.WBTORtUrK70.
[2] T.Thornhill,“A Sign of Their Be-leaf:Christians Begin Worshipping a Tree in Russia After Seeing the Face of Jesus on Its Trunk,”Daily Mail,October 2,2014,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777979/A-sign-leaf-Christians-begin-worshippingtree-Russia-seeing-face-Jesus-trunk.html.
[3] “Family See Jesus Image in Marmite,”BBC,May 28,2009,http://news.bbc.co.uk/2/hi/8071865.stm.
[4] “Citrus Christ?Man Spots Jesus in an Orange,”NBC News,January 12,2010,www.nbcnews.com/video/nbcnews.com/34823846#34823846.
[5] “Man Sells Mary,Jesus Funyuns on eBay,”Charleston Gazette,December 7,2005.
[6] D.Hume,The Natural History ofReligion,1817.
[7] For example,“How to Win Powerball Prizes Consistently,”www.lottery-winning.com/how-to-win-powerball/.
[8] R.Lustig,Learn How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Winning the Lottery(Bloomington,IN:Author-House,2010).
[9] J.A.Whitson and A.D.Galinsky,“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Science 322(2008):115-17.
[10] N.Epley,S.Akalis,A.Waytz,and J.T.Cacioppo,“Creating Social Connection Through Inferential Reproduction Loneliness and Perceived Agency in Gadgets,Gods,and Greyhounds,”Psychological Science 19(2008):114-20.
[11]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Differ on Conspiracy Theory Beliefs,”Public Policy Polling,April 2,2013,www.publicpolicypolling.com/pdf/2011/PPP_Release_National_Conspiracy Theories_040213.pdf.
[12] J.E.Uscinski and J.M.Parent,American Conspiracy Theor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3] M.J.Lerner and C.H.Simmons,“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Innocent Victim’:Compassion or Rejection?,”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966):203-10.
[14] J.V.Butler,“Inequality and Relative Ability Beliefs,”Economic Journal 126(2014):907-48.
[15] Voltaire,Épîre'l'auteur du nouveau livre:Des Trois Imposteurs”(Letter to the Author of the Three Imposters),1768.
[16] A.C.Kay,D.Gaucher,J.L.Napier,M.J.Callan,and K.Laurin,“God and the Government: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2008):18-35.
[17] K.Gray and D.M.Wegner,“Blaming God for Our Pain:Human Suffering and the Divine Mind,”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4(2010):7-16.
[18] “A Bleak Outlook Is Seen for Religion,”New York Times,April 25,1968.
[19] “Th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18,2012,www.pewforum.org/2012/12/18/global-religious-landscape-exec/.
[20] F.Solt,P.Habel,and J.T.Grant,“Economic Inequality,Relative Power,and Religiosi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2(2011):447-65.
[21] C.H.Hackney and G.S.Sanders,“Religiosity and Mental Health:A Meta-Analysis of Recent Studies,”Journal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Religion 42(2003):43-55.
我第一次有关种族的尴尬经历,是一段“往事不堪回首”的经历。当时,四五岁的我跟母亲正在逛一间杂货铺,这时,一位个子很高的非裔美国人走进杂货铺。你要知道,在肯塔基的马塞奥,几乎没有什么“种族多样性”可言,这可以说是我在电视以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黑人”。我不知道自己是被他高大的外形吸引,还是对他的肤色感到惊诧,竟然用响彻全店的嗓门大叫:“嘿,妈妈,快来看这个大……”没有人会知道我将如何说完这句话,因为妈妈紧紧捂上了我的嘴,以至于我接下来连嗫嚅的口型都没办法做出。我确实干了一件“种族歧视”的事情,但我也许只是想叫他“大个子”呢?不过妈妈没有给我任何机会,她快速的条件反射结束了一切。
当成年人表达一种歧视时,你可以指着鼻子骂他,给他贴上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仇视外国者的标签。但当一个孩子如此表达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尴尬地听着。孩子是抚养他们成长的社会的镜子。因此,当我们听到孩子们正在表达一种种族歧视时,我们为人性感到悲伤。母亲需要担心其学龄前的孩子使用此类歧视性语言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孩子会使用歧视性语言又意味着什么?
种族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富人和穷人存在于所有种族群体中,而种族歧视却影响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生活,即便他们并不穷。尽管种族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是彼此独立的议题,但它们在近些年来的交集越来越多了。因为种族不平等的进展举步维艰,缓慢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在稳步上升。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多么广泛的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种族歧视,以及对种族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用来证明和保持这种不平等的。
1619年,从第一艘满载奴隶的轮船到达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詹姆斯敦开始,种族歧视就天然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1] 奴隶制建立的一切最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奴隶制度延续了两个半世纪,比这个国家本身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当奴隶制在1864年终结的时候,一个新出台的针对黑人的法律体系使得非裔美国人又被合法压迫了足足一个世纪。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宣布公然的种族歧视违法,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明确结束了对黑人的选举权歧视。但社会变革不会发生在旦夕之间。在长达350年之久的彻底而又合法的压制之后,结束只有白人可进入的午餐档口、饮水器和学校的时间仅仅只有半个世纪,比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还短。在这半个世纪中,事情到底起了多少变化,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如果你看看民意测验,会发现美国人中支持学校隔离和就业歧视等公然的种族主义观点的比例明显下降了,从20世纪60年代的绝大多数下降到如今的个位数。这些趋势被认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但我们也许从这些趋势中得到的鼓舞过多了。
2011年,一项基于全美范围对黑人和白人的调查,要求受访者对1950年到2000年的每个10年中,黑人与白人作为歧视对象的程度进行评级。尽管白人认为自己对黑人的歧视程度降低得比黑人更快,但两组受访者都同意,反黑人歧视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下降了。然而,两组人对反白人歧视的感知差别却大得惊人。黑人受访者认为,白人歧视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不是问题,到现在就更不是问题了。与此相反,白人受访者则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在这50年中稳步攀升了。看起来,白人把歧视看成是零和博弈 [2] :他们觉得对黑人的歧视越少,对白人的歧视就会越多。这种趋势在白人受访者的眼中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他们认为歧视白人已经是比歧视黑人还严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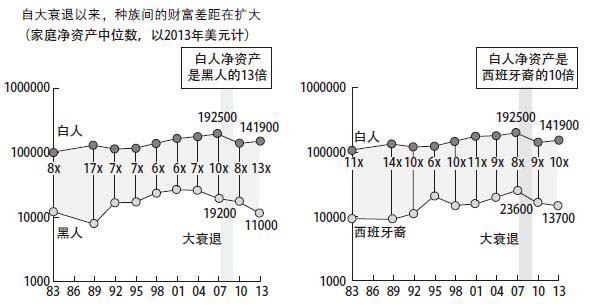
图7.1 在美国,白人和黑人、西班牙裔之间的财富差距在近几十年中仍未消除
注:黑人和白人不包括西班牙裔。西班牙裔涵盖各个少数族裔。图表是以对数尺度表示的。每一个网格对应的数量是其下面网格的10倍。大衰退始于2007年12月,终于2009年6月。
资料来源:皮尤调查中心。
然而,数据告诉我们的事实却完全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起,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就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1967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的55%。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59%。尽管由于高中入学率的普及和大学教育费用的降低,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这些进步还没有被转化成收入差距的缩小。
更加戏剧性的是,种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净额总值)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扩大的。 [3] 在2013年,白人家庭拥有的平均财富是黑人家庭的13倍,是西班牙裔家庭的10倍。这个数据与20世纪80年代差不多,但与20世纪90年代时两者之间相对较小的差距相比,还倒退了一小步。是什么阻止了教育方面的进展转化为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缩小呢?
其中一个因素是,白人家庭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比例更高。另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继承权。一旦一个家庭积累了一定财富,它就可以用来购买房屋,或者为下一代置备一些固定资产。在黑人家庭和拉丁族裔家庭里,他们的平均财富几近于零,每一代基本都要白手起家。经济学家也证实存在其他几个导致财富差距的因素,包括两者在入狱率和结婚率、离婚率上的差异。但是,在没有真正了解种族歧视——它对少数族裔家庭造成了持续的压力——所起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搞清楚这些不同。
财富、教育和房屋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可以作为一种罗尔沙赫氏试验 [01] 。如果你认为少数族裔家庭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当作这个试验的证据。而如果你认为少数族裔家庭是歧视和系统性机会缺失的受害者,你也能在这些数据中找到理论支持。问题是歧视所起的作用很难用上述数据排除。平均财富或者房屋占有率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差距的确存在,但是数字不能告诉我们差距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我们需要转向对人们行为的研究。
在一项开创性的实验中,社会学家德瓦·帕格(Devah Pager)送几对年轻人(每对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去密尔沃基找工作,以此测试现实生活中的歧视。 [4] 她给了他们同样的简历,以保证他们能够拥有同样的申请资质。她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同样的脚本,用于面试时的自我介绍和完成工作申请。接下来,这几对年轻人申请了350个工作岗位。他们并没有同时申请同样的工作;谁去申请哪个工作是随机选择的,这就形成了一项随机实验。然后,就像所有应聘者一样,这些年轻人等待着来自雇主的电话。
实验结果会支持那些“零和”思维的问卷调查受访者心中的那种反白人歧视吗?其实结果差得较远。白人应聘者得到回馈的次数是同等资历下黑人应聘者的两倍。在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其他城市进行的类似研究重复了同样的结果。除了就业领域之外,这个结果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证实。黑人租房者比同等条件下的白人租房者更有可能被告知已经没有空房可租了。比起同等条件下的白人,黑人购物者更难以低价购车,做抵押时的利率也更高。在21世纪的美国,反黑人倾向普遍地、活生生地存在。
如果问卷调查结果不能为当今的种族态度描绘一幅准确的画像,我们还可以在另一处寻找解决的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一对心理学家夫妻——肯尼斯(Kenneth)和玛米·克拉克(Mamie Clark) [5] 率先意识到:如果想要测量社会价值和预期如何潜入我们的思维,应该去观察孩子们的思维,它们是最好的文化海绵。克拉克夫妇不仅因其开拓性的调查而名满天下,也由于在大多数大学都不允许黑人与白人进同一个门的时候,他们被允许入学、毕业并最终执教的非裔美国学者身份而闻名。克拉克夫妇进入哈佛大学,随后成为第一对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他们发展了一种通过幼儿来研究种族偏见的简单途径,给一个孩子展示一对玩偶,一个是白人玩偶,一个是黑人玩偶,然后向孩子们问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哪个玩偶看起来好看?哪个玩偶看上去很丑?你想玩哪个玩偶?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白人孩子表现出了一种稳定的趋势——他们喜欢玩白人玩偶。而黑人孩子的选择则更多样,基本上被他们所处的环境形塑。举个例子,在被隔离的黑人学校里上学的黑人孩子,更加喜欢白人玩偶,这说明他们吸收了与白人孩子同样的“白人优越论”的文化信息。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取消种族隔离制时,综合学校(白人与黑人兼收)里的黑人孩子就开始不再明显地表现出对白人玩偶的偏好,有时他们还更喜欢玩黑人玩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研究者进行过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玩偶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三到七岁的儿童。在黑人孩子中,这个模型彼此之间始终充满差异,似乎与他们的地区背景和经历相关,像原始研究中的例子那样。但是对白人孩子来说,这个趋势令人沮丧地持续着:他们到现在还是更喜欢跟白人玩偶玩,跟20世纪40年代的白人孩子表现几乎一样。
玩偶研究的惊人发现是,这个跨越几十年的偏见图表,看上去更像德瓦·帕格田野实验中的那种歧视的常规模式,而不太像在调查中的变化模式。这个调查表明,偏见普遍存在,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自我报告何种程度上是可信的?当我们观察实际行为时,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偏见的存在。
更喜欢看起来跟自己长得像的玩偶是一回事,但以一种伤害别人的方式搞歧视就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情了。在因一套“阳光法案”而以透明度闻名的佛罗里达州,每个囚犯的面部照片和犯罪记录都被放在本州监狱系统的网站上,以供每个人查验。心理学家艾琳·布莱尔(Irene Blair)着手研究犯人被判刑的时间长短是否真的能够通过他们的面部照片而被预测。 [6] 她向评分者展示了上千张面部照片,这些评分者对每个犯人的罪行一无所知。他们据此判断这些犯人看上去像非裔美国人的程度,从1(完全不是)到9(一定是)打分。然后,她请了一位法律专家为每个犯人的罪行严重程度打分,同时也为他前科档案上的罪行严重程度打分。这并不是一种主观判断——佛罗里达的刑法典有一个十分制的打分体系,详细划分所有指控的严重程度。举个例子,假设冒牌驾照的罪行等级是1,那么贩卖可卡因的罪行等级就是5,谋杀就是10。这些分数被用作统计管理,研究者可以据此衡量对犯有同样罪行的犯人的判决之间有何不同。
研究者发现,在犯了同样罪行的犯人中,如果他看起来“更黑”,就会被判处更长的监禁。那些接近最高“黑色”等级(9)的犯人,会比在最低“黑色”等级(1)的犯人多判七八个月。影响评分者对“黑色”评估的特征一定也影响了判决结果。有趣的是,“看起来黑”的效果同样应用于黑人犯人和白人犯人,正如他们的前科档案上列示的那样。抛开他们的实际种族不论,其实用视觉传达的“黑色”特征可以预测判决。
即便在极刑面前,也可能存在种族偏见。在一项运用了类似方法的研究中,心理学家珍妮弗·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查阅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死刑判决书。 [7] 在20年的时间里,在600多例符合死刑判决条件的谋杀案中,浮现出一种清晰的种族差异:对独立评分人来说,看上去更黑的被告更有可能被判死刑。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在被谋杀者是白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即便在审议判决时,从不明确地讨论种族问题,但陪审团显然考虑了种族因素。
陪审席不是唯一把种族偏见变得生死攸关的地方。对勒瓦尔·琼斯(Levar Jones)来说,他的麻烦开始于2014年9月。 [8] 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一个壳牌加油站里,当他走出自己的白色皮卡时,南卡州警察肖恩·格鲁伯特(Sean Groubert)问他:“能给我看看你的驾照吗?”琼斯,这个穿着卡其色短裤和polo衫的瘦小黑人男子,这时还没关上卡车门。因此,他转身回到车里拿他的钱夹。“从车里出来!”(Get out of the car)格鲁伯特长官咆哮道。当他喊出“车”(car)这个词的时候,一声枪响在空中回荡,琼斯身后的卡车车窗被打得粉碎。
在电影中,当枪声突然响起时,发出的是一种加农炮式低沉的轰隆声。但是这个长官的手枪却发出了尖锐的砰砰声!“砰砰!砰砰!”在电影中,当一个人被子弹射中时,他看起来就像被一个看不见的拳头打了一拳一样。但琼斯先生看起来只是被吓傻了——他手中的钱包滑落,他踉跄着在钱包落地之前接住了它。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回那个向他开枪的男人。琼斯跳了起来,把腰扭向一边,看上去就像一个恼人的蜜蜂叮到了他的屁股一样。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他把双手高高举起,跌倒在地上,充满疑惑地看着地上的钱包和还在向他射击的人。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秒钟。
“我只是去拿我的驾照!你说要看我的驾照,所以我去取啊!”在格鲁伯特的射击停止后,琼斯解释道,语气变得更急切了:“就在这儿!我的驾照在这儿!”他专注地盯着自己的驾照,这是他的证据,证明“他是谁”的证据,也是证明他清白的证据和解决当前混乱的证据。当警察对讲机里不断回响“开枪了”时,琼斯问道:“长官,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朝我开枪?”格鲁伯特回答:“你违反了系安全带的规定,先生。”镇静得就像他以前也曾被这样问过似的。
勒瓦尔·琼斯当天没死,然后逐渐从臀部的枪伤中恢复了过来。格鲁伯特警官被解雇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他已经对故意伤害罪和殴打的指控服罪了。
警察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已经成为美国人关于种族话题的焦点。如果持续跟踪这类新闻,你也许会在脑海中形成这样一个画面——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已经横尸街头数小时;或者在接下来的抗议活动中,焚烧车辆的火焰照亮了好几排防暴警察的脸。当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被一名长官锁喉,濒临窒息时,你也许会听到他安静的遗言:“我不能呼吸了。”你也许会在脑海里重演视频中的模糊画面——一辆警车冲向一个14岁男孩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两秒钟后,他被撞翻在地。
所有这些事件的核心,更多的是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主观感觉。迈克尔·布朗真的袭击了官员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吗?埃里克·加纳是否恶意拒捕?塔米尔·赖斯随身带的是一把真枪吗?此类主观判断需要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做出。而在实际情况中,这样的情境经常是暧昧不明的:同样的动作,可能是去拿枪,也可能是去拿驾照。没有太多时间留给当事人对这些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如果他去拿的是枪,那么多一秒钟的思考就意味着生死两界。在所有心理学研究中最有建树的发现之一就是:人们通过依赖自己的预期,去理解不确定或是模糊不清的局面。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你仔细思考,人们更多地依赖这种预期。具有如此惊人相似性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登上头条,为我们的文化对于黑人的期望,竖起了一面不怎么讨喜的镜子。
立法决议的基石在类似“理性人测试”的案例中被奠定:当面对此类情境时,一个理性人会怎么做呢?但是,当我们正在处理我们知道的一项决议时,这个“理性人测试”就创造了许多难题,当我们回顾这些难题的时候,会发现它是错误的。尝试一下把你自己置于勒瓦尔遭遇警察的场景之中,没有人认为自己会重蹈覆辙。同样,如果格鲁伯特警官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他当然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不确定的事实是:我们都可能犯下与警察在此类枪击中所犯的同类错误。
我刚刚毕业时做了第一批实验,其中的一个——测试普通人是否更有可能相信:一个无害的东西与黑人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武器。 [9] 一个与勒瓦尔·琼斯事件十分相似的争执——一名警察向一个名叫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的手无寸铁的黑人射击,在“琼斯事件”之后成为最近的头条新闻。这位警察说他当时确实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即便最终证明当时迪亚洛手里只是拿着钱包。许多人问自己,作为一个理性人,如果自己处在这位警察的位置上,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使用了最新配备的心理实验工具,开始探索这个问题。
当时,我刚刚学会如何写代码创建一个测试此类想法的电脑程序,因此,我自己进行了第一次实验。每次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在电脑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人的照片,一些照片是黑人,另一些照片是白人。这些照片出现后,电脑屏幕上就会接着出现一种物体。这些物体中有一半是枪,另一半则是扳手或钳子这样的工具。我选择这些工具的原因是它们同样都是金属制成的,在颜色和轮廓上与枪比较类似,跟枪的大小也差不多。在每组人/物出现之后,我会按下一个标签为“枪”或者另一个标签为“工具”的按键。我把这个程序设置为重复“人脸,物体,回应;人脸,物体,回应”这个序列200次。我轻松地完成了所有200次尝试。我检查了一下我的数据,几近完美准确。
然后,我在这个程序中加入了一行关键代码:电脑开始对按下回应键的时间计时,如果所需时长超过半秒钟,屏幕上就会显示一个大大的红色X号和“太慢了!”字样。我把时间压力引入程序,它以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转换了任务——它不再是一个视觉实验,而是一种关乎瞬间决策的快速判断实验。这个实验将警察在一个犯罪嫌疑人把手伸向口袋或者回到车里时需要做的那种快速决策引入了实验室。
我又一次开始了我的实验,与上次不同,这一次的实验是艰苦的。我耸起肩膀,身体蜷缩着靠向电脑屏幕,死死盯住图片出现的那个具体的点。我越努力地去打败那个大红X,我犯的错就越多;当我为了提高正确率而更加努力时,我得到大红X的次数就越频繁。经过200次的重复后,我的脖子疼得要命,整个人像从汗水里捞出来似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太用力了,也出于我对即将出现的实验结果的担忧。数据结果显示,我的正确率在80%左右。这个结果还不赖,但是我犯错的范式很是令人困惑:闪现黑人面孔时,我更容易把无害的工具误以为是枪。
从一种角度来讲,这些数据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我对电脑程序中的黑人面孔并没有对我造成威胁是有充分了解的。而且我也知道,黑人面孔并不比白人面孔更有可能与枪支联系在一起——我只是自己写了这些代码,以保证它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当然没有理由心存偏见,而且我确实尽我所能保持准确。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数据却很能说明问题。毕竟,我成长的文化环境对孩子们使用对黑人的蔑称有着某种程度的担心,而这个文化环境也是田野调查中所有的房东和企业主成长的环境,这同样也是格鲁伯特警官成长的文化环境。
坐在实验室里,我试图战胜自己设置的偏见测试,但我失败了。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这种隐形偏见——横亘在我的良好意愿和实际偏见行为之间令人不适的鸿沟。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杂货铺里的小男孩。我在后续的几十次实验中使用这个程序,这些实验囊括了上万个调查主体。其他研究者也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中复现了这些发现。一次又一次实验印证了同样的偏见模式,当物体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时,人们更有可能把物体看成枪。在这个实验的一些版本中,我们甚至提前提醒实验对象:面孔的种族也许会使他们偏离实际,并且要求他们尽量抵抗这种歧视。但是提醒并不管用,事实上,这反而让偏见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听到这些提醒之后,关于种族的主题更加凸显在实验对象的脑海中。看来,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让我们预防无意识的偏见。
在我发表了第一项关于种族歧视威胁感知的研究之后,我收到了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来自一名退休警察,他不同意我的研究结果,因这一结果暗示了在警察群体中可能也存在这种偏见。他写道:“毕竟,我们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被迫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做出生死抉择的。”另一封信来自一位把自己描绘成公民权利活动家的人。他关心的是,通过实验证明的这种所谓“无意识的偏见”,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使那些警察免罪,而不是让他们为自己有偏见的行为负起应有的责任。关于这种隐形偏见,两位来信者可能都是正确的,这个两难困境对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了挑战。
另一种观察这个两难困境的方法,就是重新考虑“理性人实验”。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显示出了偏见,但实验对象普遍还是被种族引导而偏离了事实。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普通人是一个理性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与一个手无寸铁的白人相比,一个理性人的确更可能在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身上看到危险。那么,种族歧视在逻辑上就说得通了。但这种说法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正确”。
一种替代方法就是假设普通人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以此为前提,那么,当陪审团通过询问一个理性人应当的做法来判断其有罪或是无罪时,他们就需要一个比大多数人预期中的“防卫”程度更高的标准。但这看上去也不太公平。这就是隐形偏见的悖论,行动可以与意图相剥离,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道德义愤到底指向哪里。
要理解隐形偏见,我们需要对很容易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是“非种族主义者”的人采取一种更加细微的分辨方法。如果你考虑自己是否有偏见,以及导致你有无偏见的原因,你很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主观想法、信念、价值和良好意愿上。当你已经仔细考虑过,并认为自己是一个本质很好的人之后,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隐形偏见是其他人的问题。尽管我们都自认为是“非种族歧视俱乐部”的一员,我们却都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均建立在强大的种族不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中浸淫已久。研究显示,即便大部分好心眼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在测试中展现某种隐形偏见的迹象。
这里有一个关于另一种测试自己隐形偏见的快手示例。阅读以下文字,然后用你的第一反应完成空格。
Dog Scottish Jack Russell ________.
现在阅读第二组文字,然后用你的第一反应完成空格。
Mohammed Mosque Islamic Te ________.
我打赌第一个空格你想填的是“terrier”(梗犬,一种活泼的小狗),第二个空格你想填的是“terrorist”(恐怖分子)。我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你的信仰或是价值观的信息,就能做出这样的预测。我也不需要知道你的政治立场。我需要知道的就是你浸淫在一种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之中。结果,你的大脑也会做出同样的联系。
人类的大脑经常被拿来与电脑做比较,但人脑更像是因特网本身:一个关于思想和信息内在联系的紧密网络。就像因特网一样,这个关系网包含着不可或缺的知识,并伴随着各种杂质和无意义的东西。隐形偏见是那些在意义关联中穿行的,未经加工也未被审查的结果。而且,就像使用因特网那样,有时候,链接的另一端是干扰项。
研究指出,隐形偏见比旧式的所谓“偏见”更加普遍。尽管隐形偏见被广泛传播,最近的研究仍然显示,一些特定情境下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有偏见,而且这个差别与金钱、权力和不平等相关。认为经济地位和歧视之间无关是一种老观念。举个例子,在194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南部地区的棉花价格下跌时,被白人暴徒私刑处死的黑人数量就会增加。作者声称,当经济上的艰难折磨着白人农场主时,他们就在黑人身上发泄他们的郁闷。关于这项研究使用的统计方法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使用更精密的统计方法进行的现代分析支持了最初的研究结论:经济上的焦虑会加剧种族冲突。
如今,经济地位和种族偏见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即便它们是以一种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艾米·卡洛驰(Amy Krosch)和大卫·阿莫迪奥(David Amodio)给了白人实验对角每人10美元,用来玩一个经济学的游戏。实验对象被告知其收入本可以高达100美元,但是很遗憾,他们只拿到了10美元,从而使实验对象感到沮丧。而对照组则被告知,他们最多能拿到10美元,然后大家都拿到了,这样一来,对照组的实验对象就不会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然后,实验要求两组人都给两个人种(不是白人就是黑人)的一组照片分类。与相对富裕的实验对象相比,相对贫穷的实验对象觉得在两个人种的图片中肤色更深的人和黑人更多。处于劣势的感觉放大了他们对于种族差异的感知, [10] 增大了白人实验对象眼中的“我们”和“他们”的距离。
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处于一个更高的位置同样能够增强隐形偏见。以一项把实验对象安排成“老板”和“员工”两类人的研究为例,成对的实验对象在一个问题解决任务中工作:“老板”给“员工”下命令,然后评估“员工”的工作成果。被安排成“老板”的实验对象比被安排为“员工”的实验对象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隐形种族偏见, [11] 也比那些根本没有参加问题解决任务的控制组实验对象的偏见更强。
这些研究表明,不仅是处于劣势,处于优势也会增强种族偏见。那么,这两项发现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并不尽然。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两家公司,其雇员群体来自各个种族。公司A比较闲散,等级制也不太森严,譬如一家硅谷的创业技术公司,有乒乓球台和啤酒花园,在办公室周围还有滑板车可骑。当然,这里也有“老板”,但是她穿着牛仔裤,正在一张公用办公桌前用iPad工作,跟其他人完全一样。那么这里就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控制链。人们在一个松散的问题导向型团队里工作,当他们从一个项目转向另一个项目时,这个团队就解散了。
公司B就更加传统和等级化。在这里,有一条严格的控制链:高管坐在拐角处的办公室,给中层管理人员发号施令,然后中层管理人员再把“圣旨”传达给下层员工。如果雇员有问题,不可能有机会越级反映。
你觉得A和B哪家公司将会有跨越种族界限的更加和谐的关系呢?很显然,公司B的等级制度为偏见和冲突提供了土壤。当每个人不是处于优越地位就是处于从属地位时,等级制就会持续凸显人们在地位上的差异。等级制的效应在公司这种小范围的组织中扩散。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会更加重视地位和等级,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有更高程度的种族偏见。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一项关于警察开枪的跨国分析发现,总体说来,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遭到枪击的概率是同样手无寸铁的白人男子的3.5倍,而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中,这个概率的倍数就更高了。
收入不平等增强了种族偏见,偏见也能反过来推高收入不平等。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在厌恶黑人和反对帮助穷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之间存在着强相关。举例来说,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发现,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不平等的程度太高了,10个人中有7个人觉得政府应该增加帮助穷人的支出。然而,10个人中也有7个人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福利支出。“福利”指的是一套“种族中立”的政府项目,旨在帮助穷人,因此这些结果并不会像他们表面说的那样有意义。
但是这一研究也说明,美国人讨论的“穷人”与他们心中的“福利救济接受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种族偏见是测量削减福利经费的最佳预测器。 [12] 认为黑人懒惰、不值得给予救济的人,最有可能反对福利支出。
当然,种族偏见并不是人们反对福利支出的唯一原因。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公民之所以反对福利支出,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说得通的利益存在于此。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削减富人的税收和削减穷人的福利只是一件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事情。类似地,人们也可能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反对福利支出。他们可能更加珍视努力工作和自立自强的品质,而且把此类福利当作依赖性的陷阱,这是政治家和政治精英经常采取的立场。但是吉伦斯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想法也是普通公民反对福利支出的主要动力。从统计学上讲,如果你想预测谁会偏向于反对福利,你几乎就可以忽略他们的经济原则。你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偏见。
虽然普通人把福利看作种族歧视条款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事实是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在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中差不多是平均分布的。然而,当吉伦斯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视和新闻杂志上对福利救济接受者的描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存在着清晰的种族偏见:当福利救济接受者被描写为“活该穷”时,所指的大部分都是白人,但是当福利救济接受者被描述为“懒惰和不诚实”的时候,指的基本就是黑人了。
这个文化信息从总体上把福利同懒惰的人,尤其是懒惰的黑人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很难不在种族背景下讨论福利。这个关系激化了关于“狗哨政治” [02] 的争论,很多人在“狗哨政治”中被灌输了政客表面上的那套政策说辞,这是一种对种族偏见经过“编码”的信息。譬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著名的评论:“‘福利女王’开上了凯迪拉克。” [03] 这就激起了民主党人的愤怒,但里根否认自己的评论与种族有关。他的案例并不能对其顾问李·亚特华德(Lee Atwater)有所帮助,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李把种族编码信息作为共和党人的“南方战略”的中心组成部分:“到了1968年,你不能再说黑种人——这会伤害到你。适得其反。因此,你说强制性校车、州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现在你讨论减税的事情还是太抽象,而且你讨论的所有这些事情完全是经济层面上的事情,它们的副产品是黑人比白人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下意识地也许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3]
更近的是,白宫发言人保罗·瑞恩(Paul Ryan)被指控为“狗哨” [14] ,当他把贫困解释为“混乱的文化,尤其是在我们的内城,混乱的无业游民和一代又一代甚至不考虑工作的人……”他后来也声称,自己的评论与种族毫无关系。
我们并不确定这些领袖人物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是想要搅起白人选民心中的种族隔阂,同时保持合理的推诿搪塞能力,还是真想在反对党成员把他们的言论解读为“冷嘲热讽”时寻求种族中立?事实上,如果你支持里根和瑞恩,你就会倾向于假定他们是无辜的。但是如果你不信任他们,你就更可能觉得他们是在制造种族歧视的言论。
一个来自心理学家视角的有趣观察表明,说话者的意图实际上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观众如何解读他的言论。关于种族编码信息的概念有意或无意地假设一个受众层面的心理学跳跃。它假定当政治家讨论政策时,选民自然会把他们与种族联系在一起。最近,我与贾思敏·布朗—扬努齐(Jazmin Brown-Iannuzzi)、艾琳·库利(Erin Cooley)、罗恩·多奇(Ron Dotsch)合作检验了人们是否真的会做这个“心理学跳跃”。 [15] 我们想要确定的是,在公民被问及福利救济接受者这件事时,他们是否把接受救济者看作黑人。
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一种能让实验对象的心理表征形象化的途径。让我们从创建一张合成图片开始,这张图片分别从一对黑人男女和一对白人男女脸上选一些面部特征进行合成。在这张雌雄同体、包含两个种族特征的面孔上,我们随机加入了一些视觉干扰,类似电视屏幕上的静电干扰。我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上千次,做成一个人脸大数据库,数据库中的每张面孔看起来都略有不同,也比较模糊。然后,我们从照片库中随机抽取两张照片展示给实验对象,随后要求他们选择哪个人看上去更像是福利救济接受者。我们分别把所有被判断为“福利救济接受者”的照片混合起来,把那些被判断为“非福利救济接受者”的照片混合起来,重新创建两张新的合成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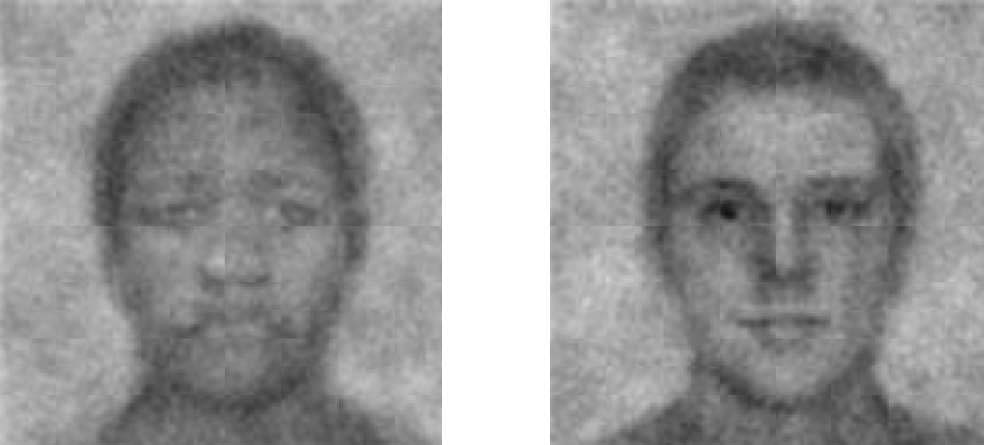
图7.2 典型的福利救济接受者(左)和非福利救济接受者(右)的形象
照片中浮现的形象捕捉了实验对象心目中的福利救济接受者形象。当我们把这两张未做任何标签的照片向一组新的实验对象展示时,他们把福利救济接受者的形象描述为一个黑人男子,把非福利救济接受者的形象描述为一个白人男子。他们觉得这个福利救济接受者看上去就很懒惰、不负责任、抱有敌意、脑子还不怎么灵光;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甚至觉得这个人缺乏人性。你能在非福利救济接受者形象的脸上看到清晰的眼睛轮廓,但是福利救济接受者形象的眼睛则是凹陷中空的。
接下来,我们测试了这些形象是否确实会造成人们对福利支持的差别。我们向另一组实验对象展示了这组典型的福利救济接受者和非福利救济接受者的形象,但没有指出他们谁是谁,然后询问实验对象是否愿意支持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和现金援助。当实验对象以为是给那个非福利救济接受者提供福利时,基本上都是同意的。但是当实验对象以为是给那个福利救济接受者提供福利时,就表示反对。人们心中评判福利救济接受者的依据,就是他们反对给这些人提供福利的依据。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种族和不平等是相互交织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基于地位的“我们和他们”的心态,这种心态加深了种族偏见。而且,这种生长在公民心中的种族与贫穷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正当性,是减少经济不平等的主要障碍。当人们觉得少数族裔是福利的受益人时,许多人就没有动力去支持反贫困。
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让许多公民感到无助,因为它看上去很难被改变。改变隐形偏见看起来尤其困难,因为它不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还存在于形成我们周围文化的人文理念的模糊现状中。然而,最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较乐观的理由。上千万人在projectimplicit.com网站上接受了隐形偏见测试,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检测自己对种族、性别、年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偏见。心理学家多米尼克·帕克(Dominic Packer)研究了美国各州展示的最高和最低等级的种族偏见以及区分它们的要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不平等。即便考虑南北各州的平均收入和地区差异值,还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州隐形偏见较少,俄勒冈、华盛顿、佛蒙特等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州,其偏见程度远远低于路易斯安那、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州。尽管要改变人们的内心和思想非常难,但经济政策在降低收入不平等上确实有用。
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了社会比较如何让我们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如何理解种族不平等。根据心理学家理查德·艾巴赫(Richard Eibach)的研究,白人公民和黑人公民之间关于歧视现状的不同认识, [16] 不仅反映了日常经验的不同,还反映了不同种类的比较。如果你询问白人受访者,美国在克服种族主义方面做得有多好,他们会把过去当作参考框架——与奴隶制和黑奴的丑恶旧时代相比,看上去的确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当你询问黑人受访者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展望未来——与一个真正平等的国家的生活相比,我们的现状看起来就相当黯淡。
然而,白人和黑人并不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研究者发现,如果你邀请黑人和白人做出另一个族群会做出的那种比较,他们最终也会同意。如果你要求黑人回想一下自己在过去所处的境遇是多么糟糕,那么他们对现状的估计就会变得更加乐观。而且,如果你鼓励白人想象真正平等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不满意,也更有动力去改变现状。请把本章的内容当成展望未来的邀请吧!
[1] I.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Slavery in North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 M.I.Norton and S.R.Sommers,“Whites See Racism as a Zero-Sum Game That They Are Now Losing,”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2011):215-18.
[3] R.Kochhar and R.Fry,“Wealth Inequality Has Widened Along Racial,Ethnic Lines Since End of Great Recession,”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12,2014,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2/12/racial-wealth-gaps-great-recession/.
[01] 罗尔沙赫氏试验(Rorschach test),是指把被测试者对10种标准墨迹的解释作为情感、智力机能和综合结构的检测方法来分析的投射测验方法。其实验原理认为一个人对墨迹图的主观描述,会将其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欲望、需求、动机冲突等反映到刺激上。——译者整理自百度百科
[4] D.Pager,Marked:Race,Crime,and Finding Work in an Era ofMass Incarcer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5] K.B.Clark,Prejudice and Your Child(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8).
[6] I.V.Blair,C.M.Judd,and K.M.Chapleau,“The Influence of Afrocentric Facial Features in Criminal Sentencing,”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004):674-79.
[7] J.L.Eberhardt,P.G.Davies,V.J.Purdie-Vaughns,and S.L.Johnson,“Looking Deathworthy:Perceived Stereotypicality of Black Defendants Predicts Capital-Sentencing Outcomes,”Psychological Science 17(2006):383-86.
[8] M.Berman,“Former South Carolina Trooper Pleads Guilty to Shooting Unarmed Driver During Traffic Stop,”Washington Post,March14,2016,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nation/wp/2016/03/14/former-south-carolina-trooper-pleads-guilty-to-shootingunarmed-driver-during-traffic-stop/?utm_term=.7354b90cf43d.
[9] B.K.Payne,“Prejudice and Perception:The Role of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Processes in Misperceiving a Weapon,”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2001):181-92.
[10] A.R.Krosch and D.M.Amodio,“Economic Scarcity Alters the Perception of Race,”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11(2014):9079-84.
[11] A.Guinote,G.B.Willis,and C.Martellotta,“Social Power Increases Implicit Prejudice,”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2010):299-307.
[12] M.Gilens,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Race,Media,and the Politics ofAntipoverty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02] 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指政客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尤其是为了掩盖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信息。——译者注
[03] 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发明了“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一词,把黑人妇女定义为专靠揩政府的油过好日子的人,其目的在于削减对于富人的税收,同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译者注
[13] A.P.Lamis,The Two-Party Sou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4] T.Kertscher,“In Context:Were Paul Ryan's Poverty Comments a‘Thinly Veiled Racial Attack’?,”Politifact,March 14,2014,www.politifact.com/wisconsin/article/2014/mar/14/context-paul-ryans-poverty-comments-racial-attack/.
[15] J.L.Brown-Iannuzzi,R.Dotsch,E.Cooley,and B.K.Payn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aliz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Welfare Recipie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Psychological Science,in press.
[16] R.P.Eibach and J.Ehrlinger,“‘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Reference Points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 Equalit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2006):66-77.
埃尔默·鲁伊斯同妻子、孩子生活在芝加哥的一个墓园中,以挖坟为生。 [1] 平时,长满草的墓地就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只有在举行葬礼时他们才必须待在家里。鲁伊斯每天挖完坟后会参加每一场葬礼,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鲁伊斯说:“我们埋葬了很多小孩,有些葬礼真的会让你悲伤落泪。”为了在这些葬礼上隐藏自己的情感,他通常会带上黑色太阳镜。
人们常问鲁伊斯是怎么挺过来的。你也许会对他的回答感到吃惊:“我十分享受这种生活,尤其是在夏天。我不认为任何工厂或者办公室的工作会比我这个更棒。我全天都在呼吸新鲜空气,这确实很美好。”鲁伊斯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
当然,你也许会反对,觉得鲁伊斯此言可能并不当真,谁会喜欢以挖坟为生呢?但你必须承认,他的回答并非不同寻常。研究者发现,“干脏活儿”的人们, [2] 如挖坟者、煤矿工人和屠宰场工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积极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起码能证明他们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享受程度并不比那些有着所谓“好工作”的人低。最近的研究发现,有95%的医生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已经是对工作满意程度最高的职业人群了。但这一研究同样发现,85%的巴士司机——算是满意程度最低的群体——同样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满意度的关键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做什么,而是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工作对人们的意义通常与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关系不大,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如何拿自己与他人相比较。
虽然埃尔默·鲁伊斯为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可怜人感到难过,其实这些人也在可怜他。当我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之后,我骄傲地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塞到信封里寄给了我哥哥杰森,就是我此前提到过的那位,当时他正在监狱服刑。他收到包裹后给我回信,说自己感到非常欣慰;他最近为自己被困在监狱,做每小时几便士的工而感到灰心丧气,直到他收到包裹,看到我每天做的事情也同样无聊,心里才好过一点。这说明我们与自己工作的关系,跟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样,都是相对的。
人们与其工作之间的古怪关系很大程度上被二战时期的美军发现了。珍珠港事件使美国陷入战争,军队在一年之内从25万人扩充到150万人。军队规模扩大了五倍之后,后勤和人力方面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柔和的怀旧之光中,今天我们记住了“最伟大的一代”的勇敢与坚忍。但当时的军队内部并非如此美好。
这些新入伍的士兵中有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军训练。官兵时常抱怨这些新兵蛋子懒散,缺乏敬意,质疑规则,而且抱怨不休。他们甚至会破坏指挥链——这在军队中闻所未闻——并且给将军和国会议员写信投诉。100万已经习惯于自由的公民与一条习惯于无条件服从的军事指挥链之间产生了激烈碰撞,被官兵称为“士气低落”的现象开始在军队中蔓延。
社会学家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涉足了这场危机,他开始领导军队的研究小分队。斯托弗使用了当时的尖端技术——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的方法, [3] 试图理清士兵的作战动力到底来自哪里。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之后,他的研究挑战了官兵们的传统观点。譬如,他发现对敌人的憎恨在驱动士兵方面的作用远远小于官兵们的估计,而不要落在兄弟连之后的欲望才是士兵奋勇杀敌的主要动力。斯托弗还发现,实战经验并不会加剧士兵对敌人的憎恨,而是惊人地降低了对敌人的憎恨——从未离开过美国的士兵对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憎恨程度远远高于那些在战场上打过仗的士兵。跟德国人战斗过的军队憎恨日本人比憎恨德国人还多,而那些与日本人打过仗的士兵则把最强烈的仇恨留给了德国人。与官兵的假设相反的还有——战争孕育了仇恨,而仇恨又加剧了战争。斯托弗发现,安全距离之外的“憎恨”比一场实战中的真切恐惧要容易得多。
当斯托弗把注意力转到研究让士兵们喜欢或讨厌其工作的原因时,他又一次发现了看上去与常识相悖的证据。他发现,与享受着快速升迁的空军士兵相比,很少有机会升迁的军警对他们的前景更加满意。他还发现,南方的黑人士兵比北方的黑人士兵士气更加高昂,即便看上去北方的黑人士兵待遇更好。这些早期发现并非侥幸。当斯托弗系统地检视这支军队的各个分支时,升迁空间最小的那部分士兵更加满足。为什么人们在这种情境中会更加快乐呢?
斯托弗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士兵的比较对象是其他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士兵——军警把自己同其他警察相比较,空军士兵把自己与其他士兵相比较。在等级相对扁平的军警队伍中,大家的军衔都差不多。但是在等级化更严重的空军里,一些士兵在军衔上的火速升迁就在普通士兵中招致了怨念。因此,“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就诞生了。斯托弗在长期的研究传统中率先发现,等级中的相对位置与特定等级的有形回报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或者说相对位置更加重要。
工作场合是大部分人每天最直接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地方。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索平等和不平等在薪酬、地位和权力方面如何形塑我们赋予工作的意义。
工作场所是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人类从事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根据这个结构安排的。在一个经典研究中,几组陌生人被带到一起,进行一小时的讨论,而他们不会被告知除了讨论之外还要做些什么。 [4] 在没有任何研究者指示的情况下,这些小组成员内部就自动分化成了“领导为讨论指明方向,其余人跟随”的等级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后院烧烤或是在街角闲逛,或是在大学教室中,只要人们聚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按照小的等级制结构将自己组织起来。更主动的“领导者”会占据更多的物理空间,发言也会更多,在小组内部沟通时也更有影响力,而更习惯于顺从的“跟随者”会听从领导者的命令。
如果日常情形都会为等级制的兴起提供土壤,那么在工作场合中更可能出现等级制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事实上,如果学者想要尝试研究一个没有等级制的组织,他们应该一个样本都找不到。举个例子,设计公司IDEO以非等级化的组织结构而闻名。当IDEO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时,它的外观和整体感觉颇有些硅谷创业公司的风范。几乎所有雇员都共享工程师头衔。即便IDEO缺少一种正式的等级制结构,当学者观察其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时发现,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异也无处不在。 [5] 竞争发生在工程师的头脑风暴环节,他们竞相提出有创意的点子,那些能想出最好点子的人自然声名日隆,于是受到大部分人的追随,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薪水。那些在头脑风暴中贡献较少的人就慢慢不会再收到头脑风暴的邀请,最终可能离开公司。这种地位、影响力和薪水上的分级,是所有等级制的核心。一些以等级制著称的公司只是比其他公司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罢了。
在某些方面,等级制可以帮助一个组织更好地运转。公司内部晋升激励也许会使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等级制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为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提供角色和期待上的清晰规则,能够减少冲突并帮助每个人定义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等级制会促使人们专攻他们最擅长的领域。以医药公司的主管为例,他们需要知道如何管理一个组织,但是他们不需要知道如何做化学实验。同样,化学家也不需要担心市场战略问题。
假设等级制的所有方面都是有利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它对商业也是有利的,说不定还觉得一个公司的等级制越厉害越好。很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等级制可以组织得很好,也可以组织得很差。而且,它看上去被组织得越来越差了。为了了解事情为何会如此,让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你觉得谁的工作压力更大——是公司主管,还是在拐角办公室外的格子间里驻扎的普通白领呢?
许多人认为承受更大压力的是那些作风强硬、A型冠心病人格的主管。他们在本应跟自己孩子在少年棒球联合会一起练习的时候,却在智能手机上回复邮件。《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位CEO的困境 [6] ——他不得不在每天早晨把自己从床上拽起来,还要召集他的团队碰面,布置他们在这一整天里要做的事情。这种情境变得很糟糕,文章告诉我们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一年,与家人一起扬帆横渡大西洋。
《福布斯》认为:“许多CEO有私人助理安排行程,而且他们总是出了一间会议室就走进另一间会议室,每天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能洗个澡。” [7] 这是一件多么耻辱的事!对于CEO来说,比膀胱压力还要大的是你必须解雇人的压力:“你可以想想,一个CEO在决定谁走人的时候是人格分裂的,这并不夸张,在一般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你必须在你周围的人中做出这种艰难的决定,这对自己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即便解雇员工的压力不会大过自己被解雇,但确实也是压力山大。事实上,经验数据完全改变了上述案例。然而,一个由心理学家加里·谢尔曼(Gary Sherman)和其同事进行的研究为领导者和跟随者感受到的压力差别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8] 他们评估了正在哈佛商学院学习管理教育课程的商业和军事领域的全职员工。参与者被划分为领导者和非领导者,领导者的工作内容是管理其他人。有关焦虑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生物性测量表明,顺应方向的人明显比指引方向的人承受着更高程度的压力。无论是从事商业还是军事领域的学员都显示出同样的结果。
等级制对处于底层的人产生压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如何以及何时做自己的工作等方面总是缺少控制力。当我本人在大学里承担一系列工作的时候,我体验过这种控制力的重要性。这些工作所需的控制力看上去一个比一个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美黄松牛扒馆”当侍应生。每桌客人的小费大约是1美元,而且小费的税会从工资中扣除,这意味着我完全是为了小费而工作。这些小费实在是太低了,我们得同时服务六到十桌才行。
我当侍应生时最喜欢的一点是时间飞逝。从我打卡上班开始,我就穿梭于餐桌之间,刚帮这桌客人点了饮料,接着就得帮上一桌客人上餐了,然后顺手再把另一桌的盘子收了,还得用余光随时关注周围情况——又有两桌客人在我这一区坐下了。上班的六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搞到最后我的脚都磨破了,但是我并不觉得疲惫;我的心仍在全速前进,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仍充斥着我的血管。
出于对心理学的兴趣,我迫不及待地在一个叫作大脑健康“危机稳定单位”的地方找了下一份工作。这家公司背后的理念是,如果每个州能避免把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中大部分都是穷人——监禁在州立医院里,那么这个州就能节省很多钱。州政府不需要为他们聘请高价医生,而是给他们租房子,聘用一名护士、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些大学在校生来照看。病人来到这里之后,常常会产生幻觉,甚至有自杀倾向。在他们拿到门诊预约号,由精神病专家诊断开药之前,我们这些人会一直照看他们,并尽可能防止他们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照看他们的第一个晚上总是令人紧张的,你等着看主要问题是否出于药品(幻觉会逐渐消失)或者是精神失常(幻觉不会消失)。
每天晚上值夜班的都是一个全职的大学毕业生,搭档一个兼职的学生。值夜班的时候,只要有新患者来到,那就是这个全职员工接新患者,留下那个兼职学生照顾几个吵闹的精神病人,同时还得接听沃伦县的自杀者打来的电话。现在回想起来,对于一个主业是他认为很“干净”的20岁心理学学生来说,这个责任的确过于重大了。我曾经接受过一些简单的培训,教你如何应对一个自杀者的求救电话,但我真正记住的也只是“陪着他们一直说话”,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马上自杀。
但有趣的是,这份工作还没有当侍应生那样让人伤脑筋。当然,从事这份工作要冒的风险有点高,但是精神病患者很少有像餐厅的客人那样要求太高的。如果你从未从事过服务业,也许你就很难理解六个人要求“胡椒先生”加饭这件事,会比应对一个有“存在焦虑”(existential crisis)的人更容易触发焦虑。而且你需要做的事比你能同时处理的事情要多的时候,就会从内部触发你的焦虑感。就像当有人在附近大声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时,你需要集中所有注意力去记住它那样。一个侍应生要应对的问题还包括时间上的压力,而且他从来不能这样回应问题:“我现在很忙,一会儿再给你回电话。”
不管怎么说,我在“危机稳定单位”的工作相比于当侍应生还是有所改善,但是这两份工作所需的控制力与我在做接线员时所需的控制力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如今自动电话菜单早就流行起来,因此我并不确定电话接听服务现在是否还存在,但如果它还存在的话,你也许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确实赶上了,因为电话接听服务本质上就是一个电话的隐形装置。
从事电话接听服务的员工会坐在一间被分成很多小隔间的大屋子里,隔间里的接线员头戴耳麦,回答着镇上几十家企业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让打电话的人知道,他已经触到了一项非业务服务,还需要创造这样一个幻象——如果他凌晨三点钟给“比利管道”(Billy's Plumbing)打电话,正等待着接他电话的是比利公司训练有素的接待员。这个剧本也许会在打电话的人开始询问一些合理问题时跑偏,譬如:“你是不是比利本人?”这时,我们依靠的就是自己曾接受的乔治·奥威尔作品中那种被称为“呼叫控制”(call control)的高级训练。“呼叫控制”是一项技能,由全世界的电话接听员和政治家实践,压制人类回答另一个人的问题的自然天性。我们的任务就是得到一个名字,一个电话号码,以及一个对于这个电话本质的一行描述,然后尽快挂断电话。
尽管我在以上工作中都没有获得晋升,而且在每个职位等级上都处于底端,然而,我对每一份成功的工作(甚至是电话接线员那个)感到越来越满意的原因是我在自己的工作和与同事的交流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力。通常,逐渐增加的控制力与更高的职级和薪水紧密相关。但是薪水不平等影响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的方式是复杂的,通常也是令人吃惊的。薪水不平等被认为是能够提供激励的。如果更多工作有成效的工人因其高效率的工作而获得了回报,理论上说,每个人就会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这种绩效薪酬(pay-for-performance)会培养出完美的经济理性。不幸的是,人们并不十分擅长遵循经济法则。薪酬不平等也许会提供激励,但是同样也会引发不满。
假设你是一名想要使用薪酬差异来驱动雇员的经理,那么你当然想在每个员工会拿到多少工资这件事情上做到完全透明。因为只有在员工掌握了这个组织里每个层级的人挣多少钱的完整信息,他们才能据此调整自己的努力程度。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公司都有或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定防止薪酬信息公开。薪金保密只有在你认为薪酬不平等在招致不满方面的效果会超过它在促进表现方面的效果时,才有意义。
薪金保密同样会在有人不能保守秘密的情况下带来麻烦。比如被爱搞恶作剧的研究人员在关于薪酬不平等影响员工的研究中泄露秘密。2008年,《萨克拉门托蜂报》(Sacramento Bee )上线了一个网站,网站上列出了加利福尼亚州每个雇员的工资。它囊括了加州大学体系的所有员工。 [9] 一个由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领衔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想法——把这个网站告知一些大学教职员工,并观察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他们给一个组织的上万名员工发送了一封邮件,提醒他们这个网站的存在,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帮助链接,通过这个链接,这些员工可以轻松查到自己和他人的工资情况。另一组人被当作控制组,研究者没有给他们发送邮件。几天后,两组人都被送到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在未来一年换工作的可能性。
很显然,这个工资网站的点击量暴涨就不足为奇了。得知同事的工资对这些雇员的工作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工资。对那些在系里处于平均工资线以下的人来说,这个信息就会使他们对工作更加不满意,并且对找别的工作更感兴趣。但是对那些处于平均工资线以上的人来说,他们的较高收入被揭露一事并没有让他们感到高度满足。事实上,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项研究实施后的三年中,研究者跟踪了那些被推送了工资网站的人,观察谁更换了工作。薪水低于平均水平的员工如今更不可能继续在大学就职了。这并非简单地出于低工资让他们有动力离职,因为控制组的低工资员工并没有如此高的离职比例。相反,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比同事的工资更低这件事。
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层员工的满意度,但也没有提升顶层员工的幸福感,这个事实对绩效薪酬理论提出了挑战。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调查实际的工作表现。薪酬不平等是否还能促进更好的工作表现?生产率和工作表现在一个大学中是很难被衡量的,因为当我们将“生产率”应用于研究者、教师和行政官员身上时,它就被赋予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含义。其他研究强调了在一些度量标准并不十分清晰的场域下的业绩问题——职业运动联盟。
在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马特·布鲁姆(Matt Bloom)记录了八年来每支“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队伍的胜负情况。 [10] 为了与“收入不平等促进更好的业绩”理论保持一致,你可能会预期,收入差距大的队伍会赢得更多场比赛。在棒球界,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几乎完全是由薪酬最高的队员推动的。那么,给球队明星以巨额薪水到底有没有增加一个球队的胜算呢?
布鲁姆的发现与这个例子正好相反。薪酬不平等程度最高的球队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球队表现得更差。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不平等程度高的球队赢得的比赛更少。这项研究同样揭示出一个有趣的细节 [11] :更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与更高的球队收入相关联。对这个发现最可能的解释是:花费巨额钱财引进超级巨星,增加了粉丝们买票的意愿,也增加了媒体对这些明星球员的关注,即便他们昂贵的合同损害了整个球队的成绩。
但是,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会损害成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会引起团队的不满,从而削弱团队合作。为了检验这个论断,我们需要把目光从单纯的胜负数中移开,更详细地调查每一个球员的表现。
研究者热爱棒球,因为有充足的数据记录了球员在每场比赛中的表现。布鲁姆查阅了初始研究的时间跨度内这个联盟中所有1664位运动员的表现数据。果然,高薪球员就是比低薪队友表现得好。但布鲁姆惊奇地发现,在薪酬不平等程度高的球队效力的巨星,表现得比薪酬不平等程度低的球队的巨星要差。如果说薪酬不平等有助于改进明星球员的表现,你的期待可能落空。高度不平等看起来会削弱本来有望对明星球员产生的激励,如果你相信薪酬不平等的主要效果是弱化团队合作与团结,那么这个结果就符合你的预期。就像在加州大学的实验那样,不平等在士气和团队合作上的负面效果大于它在业绩上产生的积极效果。
但薪酬不平等并不总是会损害业绩。在一些有关职业高尔夫球员的研究中,赢家拿到更多奖金因而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巡回赛,会有更好的高尔夫分数。 [12] 同样,关于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的研究显示,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奖金会带来更快速的比赛。 [13] 团体运动之于个人运动,譬如棒球和足球之于高尔夫和赛车,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那就是后者在有更多的奖金诱惑时,单个选手可以使精力更加集中,或是改变他的战略。但是在团体运动中,一支队伍共同合作的能力比其中任何个人的才能都更加重要。基于这个原因,不平等在团队合作上的破坏性效果大于它在某个特定个人身上的促进效果。
在理解不平等对工作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工作场所的动作到底是更像一种团体运动,还是一种个人运动。一些工作本质上是个人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卡车司机,你的职责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独自驾驶卡车,那么在你的公司里最高薪的司机和最低薪的司机之间的巨大差距也许会以某种方式,譬如更长的工作时间,来促进更好的表现。但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大部分工作需要团队合作。甚至像电脑编程等相对个人化的工作,通常也是团队工作的一部分,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更大的工程,至少在一部分时间内是这样的。
不平等影响团队表现的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体育运动。针对几十个公司的大型研究比较了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 [14] 产品质量由每种产品领域的专业第三方主管评定。他们发现,主管与小时工之间的薪酬不平等程度越高,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就越低。大多数产品是由一个漫长且复杂的生产链制造的,其中包含了这个公司内部各个层级员工之间上万次的交流。一个工种越像一个团队,对不平等的不满等负面效果就越会抹杀它刺激业绩提升的效果。
实际上,雇员想要的也并不是平等。他们明白,接受过高级训练,有技术和经验的人应该比那些技术水平低的新手工人得到更高的工资。人们期望的是在他们的付出和回报之间有一个公正的平衡。如果用比率描述这个平衡,其中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时薪。然而,除了钱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回报,以及除了工作量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贡献。
当回报与贡献之间的比例失衡时,人们就会尝试去矫正它。关于这个特定的公式,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增加回报和减少贡献都能使大家满意。在时薪这个例子中,意味着提高工资(为同样数量的工作)或者减少每小时的工作量(为同样的薪酬水平)。当雇员感到他们并没有得到与工作相适应的补偿时,就会协商要求更多的工资和福利,当这种协商不起作用或者是干脆不可能时,他们就会在手段上变得更有创造力。
他们可以偷懒,接受马丁·斯普劳斯(Martin Sprouse)采访的一名大学维修工人亚当就这么认为:“我们总是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我们维修工人,这所大学横跨整个城市,我们戴着工作手套,开着有大学校徽的卡车,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必请示主管的情况下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通常开着卡车去一个同事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去打卡下班。” [15]
改善这种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盗窃提升工资,酒品仓库的装运员罗伊就是这么干的。罗伊所在的公司从波士顿迁到了路易斯维尔,计划解雇所有员工。根据罗伊的描述,这两件事“完全摧毁了整个工厂的士气”。罗伊的职责之一是巡视仓库,捡出被其他员工喝了的半空酒瓶子。罗伊把最便宜的那些酒瓶子丢掉,然后把最好的酒瓶留给自己。“每个月我们都会拿出目录,追踪这些‘损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些‘饮耗’……最后,装运部门的这些员工决定,他们也许也应该自行安排自己的遣散费。在上班的最后一天,我们本该把所有的库存装到一个货车车厢中,把它发到肯塔基去。我们没有照做,而是把200箱不同种类的酒装到一辆小型货车上,然后开着它去镇上的各个地方,停在所有工人家门前。当小型货车再回到工厂时,它已经空空如也了。我到现在还存着些酒呢……”
为了修复这个平衡,有时需要采取一些更加隐蔽的手段,就像基金经理P.J.K.所说的那样:“我看到了那些人偷的钱,而且我也想分一点。”一天,他发现自己可以通过交易大厅里的共享电话实施更大规模的交易。“我接了一些电话,按下一连串按键,然后跑到德励(Telerate)的大屏幕前,观看市场暴跌……它变成了一个大游戏,而且我享受在这个交易部门捣乱,然后跑到大屏幕前看市场波动的过程——我询问交易员是否能使用一下他们的电话,获得同意后就接上电脑连线,只需要用拳头乱锤键盘就行,这太有趣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贼还是盗取了利益,但彻底的破坏也会导致无意义的毁灭。斯普劳斯的研究对象中包括破坏了一整箱信件的邮政员工,还有把手套放到切片机里搞破坏的凤梨包装工人。其中最邪恶的破坏者是一名汽车厂工人,他把铅笔芯放到化油器里,这样它们就会到处漂,导致汽车间歇性地熄火……而这看上去都是些令人心烦的随机事件。这些行为看似无理性,除非我们想起人们希望获得的那种“平衡”。通过此类消极做法改变贡献收益比并不会让你的账户多出钱来,但是它能在情感上达到一定的平衡。正如那个大学修理工亚当所说:“如果我非要为这种做法找个理由的话,我会说这并不是由复仇驱动的,仅仅是出于付出与得到的公平起见。”
研究人员分析了数百次斯普劳斯采访,归纳了“坏行为的动力”,他们发现,不公平感和控制力的缺乏弥漫其间。尽管这类叙述只是道听途说,但另一项实验则更加系统地考察了不公平如何驱动工作中的坏行为。研究者与一家经营三家工厂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合作。这家公司最近丢掉了它与一个大客户的合同,而且不得不开始削减员工工资,直到补上损失的收入为止。研究者说服了这家公司,让这个痛苦的减薪历程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实验。 [16]
在其中一家工厂,经理把合同签丢这件事告诉了员工,并且告知他们,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他们会被减薪15%。在另一家工厂,经理并没有给员工减薪。然后,研究者与公司会计一同衡量这些工厂的库存资产会缩水多少。换句话说,他们要记下工厂有多少商品和设备会离奇消失。
在减薪前的10周中,两家工厂资产缩水的比例相同,工厂中不到3%的商品不见了。但在减薪的10周中,不幸遭到减薪的那家工厂的资产缩水量是平常的3倍。为了证实他们观察到的结果确实是减薪带来的,研究者在恢复正常工资后的10周里继续监测资产缩水情况。结果发现,偷盗率回到了减薪前的水平。
这些雇员偷盗的原因是他们需要更多的钱维持生活吗?还是这种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感觉激发了他们把盗窃当成扳回比分的途径?我在前文曾提到过,还有第三家工厂,研究者用这家工厂来说明偷盗事件增加的原因。这家工厂的管理人员也被减薪15%,但并不是直接宣布减薪措施。管理人员向员工说明了减薪的背景和原因,解释只有通过降低所有人的薪水,才能避免解雇员工。而且,这家工厂的经理强调了他与整个管理团队的减薪幅度会与其他员工一样。在这家工厂减薪期间,其偷盗率只有轻微上升,一直保持在5%以下。正如这些结果显示的,当工人认为回报之于贡献的比例不平时,偷盗主要是调整回报贡献比的一种做法。
我们已经看到,当工人们正在经历控制力丧失时,他们就会感到压力,在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压力就更大了。减薪一定会产生不公平感,同时,能达到这种效果的方法还有很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判断自己的薪水,这表明近些年来普通员工停滞不前的工资与主管们不断攀升的工资加剧了不公平感。
针对加州大学员工的研究说明,只有在工人们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的时候,他们才会对此感到不满。最近在美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都说明,人们只是没意识到大部分公司有多么不平等罢了。有研究调查了世界上40个国家, [17] 要求受访者估计本国普通无技能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和本国一家大公司总裁的平均工资。然后,研究者发问:“你认为员工和总裁理想的平均工资该是多少?”完成了这两个问题的统计之后,研究人员计算出了CEO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比率。
在每个国家,人们对不平等的预期要低于他们对实际不平等的估计。平均来说,受访者认为CEO的工资应该是普通员工的10倍。与此相反,他们的理想状况是CEO的工资最多应该是普通员工的4.6倍。在这些发现中,最令人震惊的方面之一是取得共识的程度。自认为在政治上偏左的人认为,CEO的工资最多应该是普通员工的4倍,而那些把自己归为右派的人则认为理想的比例应该是5倍。收入处于底层20%的受访者认为CEO的工资应是普通员工的4.3倍,而收入最高的20%受访者则认为5倍比较合适。人们的理想模型竟然惊人的一致,跨越了年龄、教育水平和研究者检验的每一个变量。
只有在对实际存在的收入不平等令人震惊的全球性忽视之下,实际的收入不平等才会远远超过人们在工资不平等的心理预期方面的全球共识。在每个被调查的国家,受访者都戏剧性地低估了工资不平等的实际程度。以美国为例,人们估计CEO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30倍。研究人员指出,2012年,CEO的平均年薪是1230万美元,普通员工的平均年薪是3.5万美元,CEO的收入大约是普通员工的350倍!
美国人认为,CEO的年薪是100万美元。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标在引言里的人形收入分布图上,它标记的位置只不过是在胳膊肘上方。然而,要想标出年薪1200万美元的实际价值,那就需要在这个人形的头顶上再加八个人的高度。工人自然不会期望CEO只挣3.5万美元,就像他们也不会指望自己能挣1200万美元一样。但是350∶1的比例也足够挑起大部分人心中的不公平感。尽管在一家公司中,顶层高管的价值比普通员工高很多,但他/她真的就值350倍这么多吗?
想对一名CEO的实际价值进行量化是很难的,但是有很多研究已经可以对此做一些粗略的估计。研究人员基于对一些公司的业绩进行的多年调研可以辨别出,一家公司的财富有多少与它的掌舵人相关。假设一些CEO比其他CEO的表现更好,这看上去是合理的,而且那些被其中最优秀的CEO掌舵的公司会挣更多的钱。但在决定挣钱多少的因素中,有很多是CEO也无法控制的。如此说来,一个顶尖高管到底对一家公司的成功起多大作用呢?
管理学专家马库斯·菲特扎(Markus Fitza)对上万家企业进行了近20年的综合分析,他发现,这些公司只有5%的业绩表现差异可归因于CEO, [18] 而其他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经济波动影响商业表现,对此CEO束手无策。银行业等比农业之类的产业更加有利可图。而一些公司在现任CEO上任之前就比其他公司成功得多。菲特扎预估,除这些不可控的因素以外,一家公司约有70%的业绩纯粹是随机的,而这往往是CEO通常受褒奖或受指责的内容。当一家公司决定寻找一位新的CEO时,一般都会雇用猎头和咨询公司,花上几个月和几千万美元挑选最合适的候选人。菲特扎的研究指出,他们当然会确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的人选都具备这份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但接下来要做的也仅仅是从中随机选取一个名字而已。
人们一般接受不了他们关心的结果是随机产生的。各种研究曾反复证明,专业的股票投资人也无法持续稳定地预测某个反映了整体市场的指数基金;苏打水死忠粉在盲饮的时候也不一定分得清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19] 被蒙上眼的专业小提琴师也不能区分他们正在演奏的是斯特拉迪瓦里提琴(Stradivarius)还是普通小提琴。 [20] 而且,人们有多少时间和努力会献给选股票,买著名品牌的苏打水,或者为了有机会演奏售价300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提琴而节俭一辈子呢?
菲特扎的分析结果引起了争议,这并不出人意料。 [21] 但其他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重新分析这些数据后,发现这种CEO效应可能要高达22%。其他研究的估计落在5%~22%的某个位置上。暂且不论这些真实数据的结果到底是接近5%还是22%,要让员工确信他们的CEO“物有所值”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今,与CEO薪酬相比的极端不平等很有可能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团队表现和生产质量,并有可能激发员工偷懒、偷盗和搞破坏。到目前为止,由于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薪酬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这些倾向也许还没有出现。但是,当CEO的薪酬达到一个新高度时,那就会越来越为公众知晓。
2015年,公司第一次被要求公开披露CEO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比。现在要证明这种信息公开会对员工的士气有何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很显然的是,公众对薪酬不平等的觉醒已经开始抬头。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CEO的薪水实在太高了, [22] 而且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CEO的薪水应该设置上限。想象一下,一旦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又会发生什么呢?
[1] S.Terkel,Working: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New York:New Press,1974).
[2] B.E.Ashforth and G.E.Kreiner,“‘How Can You Do It?’: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1999):413-34.
[3] T.F.Pettigrew,“Samuel Stouffer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8(2015):7-24;J.W.Ryan,Samuel Stouffer and the GI Survey:Sociologists and Soldier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2013).
[4] P.E.Slater,“Role Differentiation in Small Group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55):300-310.
[5] R.I.Sutton and A.Hargadon,“Brainstorming Groups in Context:Effectiveness in a Product Design Firm,”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1996):685-718.
[6] L.Kwoh,“When the CEO Burns Out,”Wall Street Journal,May 7,2013,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687604578469124008524696#articleTa bs%3Darticle.
[7] K.Kneale,“Stress Management for the CEO,”Forbes,April 17,2009,www.forbes.com/2009/04/16/ceo-network-management-leadership-stress.html.
[8] G.D.Sherman et al.,“Lead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Stress,”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09(2012):17903-07.
[9] D.Card,A.Mas,E.Moretti,and E.Saez,“Inequality at Work:The Effect of Peer Salaries on Job Satisfa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2012):2981-3003.
[10] M.Bloom,“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Pay Dispersion o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42(1999):25-40.
[11] M.Mondello and J.Maxcy,“The Impact of Salary Dispersion and Performance Bonuses in NFL Organizations,”Management Decision 47(2009):110-23.
[12] M.Melton and T.S.Zorn,“Risk Taking in Tournaments,”Managerial Finance 26(2000):52-62.
[13] B.Becker and M.Huselid,“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ournament Compensation Syste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992):336-50.
[14] D.M.Cowherd and D.I.Levine,“Product Quality and Pay Equity Between Lower Level Employees and Top Management:An Investig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992):302-20.
[15] M.Sprouse,Sabotage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Anecdotes ofDissatisfaction,Mischiefand Revenge(San Francisco:Pressure Drop Press,1992).
[16] J.Greenberg,“Employee Theft as a Reaction to Underpayment Inequity:The Hidden Cost of Pay Cuts,”Journal ofApplied Psychology 75(1990):561-68.
[17] S.Kiatpongsan and M.I.Norton,“How Much(More)Should CEOs Make?A Universal Desire for More Equal Pay,”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2014):587-93.
[18] M.A.Fitza,“The Use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EO Effects:How Large Must the CEO Effect Be to Rule Out Cha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2014):1839-52.
[19] M.E.Woolfolk,W.Castellan,and C.I.Brooks,“Pepsi Versus Coke:Labels,Not Tastes,Prevail,”Psychological Reports 52(1983):185-86;S.M.McClure 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Preference for Culturally Familiar Drinks,”Neuron 44(2004):379-87.
[20] D.J.Levitin,“Expert Violinists Can't Tell Old from New,”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11(2014):7168-69.
[21] T.J.Quigley and S.D.Graffin,“Reaffirming the CEO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Much Larger Than Chance:A Comment on Fitza(2014),”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M.A.Fitza,“How Much Do CEOs Really Matter?Reaffirming That the CEO Effect Is Mostly Due to Cha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
[22] J.Jones,“Most Americans Favor Gov't.Action to Limit Executive Pay,”Gallup Poll,June 16,2009,www.gallup.com/poll/120872/americans-favor-gov-action-limit-executive-pay.aspx.
书中的每一项研究,都检视了不平等的某个方面。为了推动科学的进步,确有必要把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一些简单的部分,并弄清楚它们分别是怎样起作用的。但是这些部分最终要被组合成一个整体,因为真实的生活远比任何单一的研究都更加复杂。
“快生早死”的方式是由不确定的未来驱动的,它指向短视的决策,从发薪日贷款到贩卖毒品再到辍学,这些短视行为虽然提供了短期回报,但牺牲了长远的未来。它还怂恿青年人尽快生小孩,并贬低婚姻的价值,结婚往往是大部分人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长期决定。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同样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破坏。我们的压力和免疫系统对日常危机的应急反应赋予我们走出那些糟心事的能力,但其代价是牺牲我们未来的福祉。这种由贫困引起的不安全感,与由不平等引发的“我之于他”的简单对抗观念,共同触发了人们接受简单的信仰、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提供简单回答的偏见,从而破坏公民社会的健康运行。
以上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会强化原始的不安全感和危机状态。在这个动态中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能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人和那些努力摆脱困境的人,把那些身负最糟糕的问题、前景也最黯淡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这部分人被社会学家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称作“真正的弱势群体”。人们倾向于从他们熟悉的选项之中做出选择,从而走上一条看起来相对好走的道路。一个出生于恶劣环境中的孩子的交友圈里不可能会有那些上了大学的孩子,也不会有穷人以外的人。这些自我强化穷人身份的因素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地心引力,让任何想逃出这种引力的行为变得难上加难。
地心引力的比喻是很贴切的,因为想要逃离劣势集中区就必须达到我所说的那种“逃逸速度”。在物理学上,逃逸速度是逃离一个星球的重力牵引所需要的最低速度。当离开地球的火箭达到这种速度时,它就能永远运行下去。当人们逃离一个贫穷的环境时,也要做到某种意义上的“永远离开”。即便他们最终又回来了,他们的思维和谈吐也会有变化,甚至连饮食都与先前不同。我的一个家人曾经跟我说,她不想为自己的孩子设立教育基金,因为那些上过大学的人最终都变成了无神论者。而且,与受到“永恒的诅咒”相比,即便收入潜力增加了又有什么用呢?
以我自己为例,我决定逃离贫困区,但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除了惯常的节日访问以外,我与家人可能再也不会像留在肯塔基州的那些兄弟姐妹之间那么亲近。我女儿不会像住在爷爷奶奶家路那头的孙儿们与爷爷奶奶那样亲密。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意味着我和家人之间在认识世界运行方式上鲜有共识。假期聚餐时的话题必然在政治、宗教和当前新闻事件上游走。我与我的家庭之间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是可预测的——事实上,是通过此前几章展示的科学研究进行预测的。这些科学研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着不同经历的人会对这个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是,教育程度和财富上的差别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推得越来越远,那些差别在不可打破的文化壁垒中变得越来越固化。
了解不平等如何加速劣势的循环,可以帮助解决人们讨论不平等时产生的很多争论。下面我将以我的叔叔斯特曼的生活方式为例对此加以解释。斯特曼叔叔生活在县城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冬天的夜晚,气温接近零度,这时我父亲就会去看看他,并尽力说服他去我家过夜。但是斯特曼叔叔坚持留在自己的谷仓里,始终蹲坐在谷仓一角的煤炉旁边。小时候,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黑人,煤炉里的煤渣和垃圾场的污垢二者的共同作用,已经让他变得黝黑。有一次,我父亲成功地说服了他,让他跟我们住了一阵,但是他拒绝住在我们的房子里,而是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住在我家的谷仓里。这个地方前几年曾被当作猪窝,我父亲怕脏,就在其上又建了一层,并给它盖了一个红色的顶棚。父亲还在谷仓里装了电灯,在墙上镶了木板,谷仓看上去就更像一个家了。但我叔叔在这里只住了几个月,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他天天以“芝士涂鸦”(Cheez Doodles)和威士忌为生。后来,他又回到了自己原先住的垃圾场。
如果你想要把我以上的表述解释为对斯特曼叔叔个人行为的控诉,那么你就很容易认为只要他戒酒,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回到工作岗位上,就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很显然,是他的选择导致了处境的每况愈下。但是这种论断又不能真正说明任何事情,因为你可以立即反问:“为什么有人会坚持这样的行为呢?”自我毁灭式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因为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从一个更高价值的结果转向一个更差的结果,这是非理性的。为了理解斯特曼叔叔的选择,你需要了解他是如何看待自身处境的。你需要知道他面临的日常危机是什么,他的梦想,他的遗憾,他的失落,以及他抚平心痛的努力。换句话说,你需要了解他陷入的破坏性循环是什么。不止这些,你还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地方,像斯特曼叔叔这样生活的人肯定更多。
当人们在斯特曼叔叔这样的个人行为和不平等来源等系统性因素之间展开争论时,仿佛这个问题是一个“二选一”式的辩论,其实他们弄错了重点。不平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行为上的差别又会扩大不平等。虽然许多研究过穷人生活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贫困和自我打击的行为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循环,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似乎都会在开始提出解决方案时,迅速忘记这个等式的某一边。
保守派关注个体的能动性,认为必须通过奖励措施以驱动下层人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穷人的行为其实由更加急迫和重要的动因驱使。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日常危机,因此他们会试图用手头最好、最短期的危机管理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危机。他们早就放弃遵循经济学家所说的对奖励措施的理性回应,而是采取了旨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行为。如果你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中,要求你“振作起来”的劝诫,听上去就很空洞无物。
左派认识到收入不平等和遗传性劣势等系统性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经常过于小看个人决策在他们的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个人状况部分是由环境和社会结构所致,这一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他们能认识到,对任何特定个人的系统性影响会反映在人们基于日常逻辑做出的具体选择上,那么他们对系统层面上的抽象解释对大部分人来说就会更有说服力。
后来,我叔叔在那个垃圾场的谷仓里度过了他短暂的余生。在他59岁那年,在持续了一生的吸烟、酗酒和艰难生活之后,他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他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因为医生告诉他不能同时吃止疼药和喝酒。他选择了威士忌。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命运。
无论是处在政治光谱哪一边的人,都会认为没有什么能够修复这种持续的有害行为。一旦一个人死死地陷入自我摧残的循环,想要把他从中拉出来,也许的确很难。但是甩手声称这种境地无望改变,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逃避的行为了,它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的行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反映。而环境实际上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像我叔叔那样在一个泥地上的小屋里长大,一家子不是矿工就是佃农,人们做出错误选择的次数就会更多。人们在美国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比在加拿大这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要高。这种选择上的差异甚至存在于不平等程度不同的州之间,譬如高度不平等的肯塔基州和不平等程度较低的艾奥瓦州,然后转变成人们生活状况上的显著差异。
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如果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今天,对你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很可能是在一个诚信投资能得到回报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你觉得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你可能是在一个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世界中长大的。而且,如果你在某种压力事件结束之后,能够保持稳定的压力反应,那么你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世界中生活了。如果你有幸以此为人生的“默认设置”,那就会随着一个上升的螺旋而上升。你的未来很可能是光明的,因为在现代经济中,你的本能就是那种富有成效的类型——目标在于长远的成功,而非当前的危机管理。
我的女儿一岁左右时发现了一种能吓唬父母的游戏。她会蹒跚着爬到床或沙发的边边,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把自己甩下床或沙发,对附近总有人能接住她充满信心。为了接住她,我的膝盖和胳膊肘多次擦伤,但是她的确从未掉到地上过。我知道,我的干预只能鼓励她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但是我也实在不能不管她,让她以如此冰冷的方式知道这是个危险的游戏。一来我担心她可能真会受伤,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相信,她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当她铤而走险时,会有人接住她。我希望这件小事能把她的预期循环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
直到最近,贫穷的循环仍被认为只是物质匮乏所致。而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相对贫穷和不平等对贫穷循环的推动相比于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同样重要。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书时,他们同我分享了自己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当我把这个项目告知我的同事时,他们给我发了许多关于贫穷对大脑和身体产生作用的科学论文。没有人提供关于他们城市最富有的人的信息,也没人提供讨论棒球明星或是银行高管工资的文章。但是不平等对富人追逐财富的驱动力,与它对穷人陷入贫穷的驱动力一样大。
只要考虑当代社会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的影响,你会很自然地把目光转移到穷人身上。当一代名贼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被问到抢银行的原因时,他很可能这样回答:“因为这里有钱啊!”如果我们询问人道主义者为什么会帮助穷人,他们或许也会说出类似的答案:“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啊!”无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现实原因,摆脱贫困自然都是首要目标,因为贫穷能摧毁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发展中国家,贫穷剥夺了人们的基本需要,这个问题显然比不平等有更高的优先级。但在发达国家,贫穷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它不仅仅是你身上有没有衣服穿的事儿,而是在你送孩子去上学时,他会为自己没穿上名牌服装而感到羞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战胜贫穷是首要的,但这也只是万里长征走了一半而已。
务必严肃对待不平等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说明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我们无法简单地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就像人们经常把不平等和贫穷混为一谈一样,他们也经常把降低不平等的目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混为一谈。但是研究发现,不平等本身在健康、决策制定、政治和社会决策等领域影响深远,要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光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不平等在统计学上的反映,譬如基尼系数,几乎完全由富人的富有程度所致。即使有那么几个经济学天才能提出一些创见,让每个人的收入在一夜之间翻番,也不会让不平等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反而会使它更加严重,因为百万富翁的收入翻倍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会远远多于那些年薪15000美元的人收入翻倍的所得。虽然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是不平等的问题也变得更加明显。
你在生活中也许会发现:人们的幸福感随着他们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幸福感可以被看作反映一个人总体生活的情绪晴雨表,就像它能测量我们在这几页论述中关注的许多健康、压力和社会指数那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特定国家内部,富人更加快乐,但也只是比普通人高了一个百分点而已。2010年发布的一份大型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人幸福感的拐点大概是75000美元。收入在这个数字之上时,金钱在幸福感上的正面作用就开始下降 [1] :那些年薪800万美元的人并不比年薪8万美元的人更开心。
由于美国大部分人的年收入都不到75000美元(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大约是54000美元),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逻辑得出结论:更大程度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增加普通人的幸福感。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经济增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当人们的收入增长后,他们很快就会适应更高的经济地位,而其收入的每次增长都会变成新的常规起点。结果,普通人的幸福感就会完全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无关。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 [2] (Easterlin paradox)而为人熟知。
以标准的经济指标来看,刚刚过去的50年对美国来说是一段相当有利的发展时段。美国的GDP每年都在增长。如果你浏览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均GDP,你会发现它的增长是直线飙升的。即便是在2008年最痛苦的经济危机和随后而至的大衰退中,人均GDP也只是下降了一点点而已,而从那以后,人均GDP又开始持续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是构成幸福感的最关键因素,那么我们都应该过得非常愉快。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美国很难再做到让人更不满意了。我最近在罗利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听到了坐在我后排的两位女士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让我完美地抓住了一种弥漫全国的情绪。年长的女士用波士顿腔评论道:“这太差劲了!一切都太差劲了!经济情况太糟糕了!犯罪太猖獗了,因此我每天只是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甚至从不外出!”她旁边那个操着南部口音的年轻女士非常理解地感叹道:“是这样,这让你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俩人还是能付得起机票钱的女士呢!她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富有的国家的两个极丰裕的城市之间旅行,现在还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犯罪率最低的时刻。 [3] 但很显然,她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理解“伊斯特林悖论”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被广泛地分享。就像本书引言里所说的那样,增长带来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到了最富有那部分人的腰包里,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则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幸福感受相对地位的影响,而不平等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落在了后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高度不平等就是比GDP更好的不幸福预测器。这个结论正是由心理学家大石茂弘(Shigehiro Oishi)领导的团队在查阅1972—2008年美国人的幸福感波动曲线时发现的。 [4] 家庭收入并不与幸福感完全挂钩。但是,当收入不平等年复一年地上升或下降时,不幸福感也会随着它上下起伏。
大石的研究发现,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链条在穷人之间是更坚固的,但它同样也影响到了中产阶级。事实上,这个链条影响了除最富有的20%之外的所有人。但是像收入不平等这么抽象的东西又是如何成为影响人们日常幸福的因素的呢?是一套特定的信念充当了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桥梁。在不平等程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们更容易认为其他人都是不能信任的,而且一有机会就想冒险。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能预测不幸福。
不管怎么说,经济增长总是比经济停滞更受欢迎。但是,只流向最富有人群的经济增长将会加重不平等。那么,我们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呢?有关不平等循环和我们对不平等的行为反应方面的科学发现表明,不平等有两条解决途径,我认为我们应该双管齐下。其中的一个关注点是社会背景,而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回应。第一步可以先建造一个比较平缓的社会阶梯,第二步就是让生活在阶梯之中的人们过得更好。
很显然,缩短阶梯,即减少不平等,是解决许多已知问题最快捷也最有力的方法,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会促进其他很多问题的解决。一般来说,政策专家一次会集中寻找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医学专家寻求改善健康状况,犯罪学家规范政策以减少犯罪,教育专家设计改善学校教育的方法,等等。当然,我们面临的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有其独特的面向,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是其中很多问题的共同本质,如果不直接解决极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而是迂回地提出其他方案,都是愚蠢的做法。人类历史上两个最有效的公共健康成就是抗生素的发明和公共卫生系统 [5] (污水管道系统和含氯自来水)的建立。这些创新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并在20世纪奇迹般地延长了人类的生命周期。它们并不是靠消灭某种单一菌落或是预防某种疾病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它们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于它们能全面地应对上万种感染病。
类似地,减少不平等也有一次解决大量问题的潜力。但是这需要把不平等从说教的镜头下移开。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把不平等看作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在实践层面,减少不平等意味着提升社会阶梯最底端的那一级,同时降低社会阶梯中最高的那一级。许多著作已经讨论过旨在采用上述做法的各类政策的实质。其中一些措施受到左派的支持,譬如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儿童早期教育,限制行政支出,加强联合以及增加带薪产假等。其他依靠市场力量减少不平等的动议对保守派和自由派来说也许更具吸引力。以巴雅·莫汉(Bhavya Mohan)领导的一项研究为例,他们发现,当消费者得知一家公司的CEO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水高度不平等时, [6] 他们就想通过购买其薪水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以达到惩戒效果。
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受到更大多数的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举例来说,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会支持扩大劳动所得税减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以补贴贫穷工作家庭的动议。自由派欣赏这项政策,因为它为穷人提供了福利,而保守派支持它的原因则是它对努力工作者给予回报。更戏剧化的是,为穷人提供基本的保障性收入同样也受到进步人士和自由派的拥护。 [7] 自由派的吁求是,一次性提供金钱的方式会比通过一大堆独立的政府行政项目来提供福利更有效。
当我主张不平等主要是一个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时,我曾多次在课堂上遭到反对。有一天,一个学生朝我大声喊道:“你说的东西简直就是社会主义!”对于任何偏离将未受监管的市场作为促进更大程度的平等的观点来说,这个学生的观点都是一种普遍的回应。但是这种论断漏洞百出。正如要求减少酗酒并不是“禁止”喝酒,号召限速也不是要努力让交通放慢到爬行一样,倡议降低如今的极端不平等,也并不是在倡议一种社会主义体系。
一些语境是有序的。我们在第二章全景式地扫描了各种社会问题,从青少年生育到高中辍学率再到暴力犯罪,这些社会问题在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州都更加明显。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看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更大的平等与更长的寿命相关,在州与州之间比较的结果也是如此。这些统计分析显示,从肯塔基州或是路易斯安那州到艾奥瓦州或犹他州,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努力都会改变千万人的生活。艾奥瓦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天堂,但是对其公民的寿命和生活预期的测量结果却比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州要好很多。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消除所有不平等,这不仅过于理想化,也不可操作。乌托邦的理想有可能变成反乌托邦的现实。而且,我们的目标只是把不平等程度调整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范围之内,这将给人们提供更加充裕的空间,以完成并推进他们的生命历程,而不是仅仅把经济竞争变成“赢家通吃”的竞赛。在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程度是竞争的自然结果,市场竞争中总是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许多人基于这个基本点进行推断,但其目的是要得出既然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社会流动有利,那么更高程度的不平等一定会更加有利的结论。
事实证明这种逻辑是彻头彻尾的倒退。正如我们熟知的盖茨比曲线(Gatsby curve) [8] 揭示的关系,实际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州和地区的向上流动性更小。稍稍转换一下观察的视角,你就会发现,这意味着你生活的地方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你的经济前景就越受制于你父母的财富,而非你个人的成功。当经济阶梯的横梁之间分得越开时,要爬上这些横梁就变得更难。
改变经济地形的基础是保持长远的眼光,但是关于不平等的科学研究还提出了意图更直接地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其他策略。其中第一个策略就是明智地选择社会比较的对象。 [9]
我此前曾主张,社会比较是日常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我们把自己与其他人混杂地加以比较,而且这种相对比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据此判断一切,如果我们总是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在这样做的事实,那么我们如何明智地进行比较呢?
传统观点认为,这种无意识的思维并不是不可能进入的地方,就像被隔离的“弗洛伊德的洞穴” [01] 那样。如今,心理学家认为大部分无意识的思绪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本能。我们可以用阅读为例对此进行很好的阐释。你第一次了解如何把字符串解码为文字的过程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这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学习。但是,当你在这方面的技术越来越好时,阅读就变成自动的行为,而不需要费力。你不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读出音节,把音节连成单词,再把单词连缀成句子来获取意义,即便这个过程的确是你的大脑在运作。让我们再换个角度,当你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你同时也在呼吸,或者你的臀大肌正在承受的压力大小。我们会对不再需要花精力关注的规律性活动失去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主动引导自己关注这些规律性活动以此感受它们。就像呼吸,一旦我们注意到它,就能经常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施加一些控制。
有一个信号能证明你正处于无意识的社会比较的控制之下,那就是对“你拥有的事物不够好”的一种模糊的焦虑。我们总觉得自家厨房的层压台面有点问题,因为它不是花岗岩质地的,或者不是上好的花岗岩——大理石做成的。从居住的房子到脚上穿的鞋,我们总是在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做类似的算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到底什么才算“足够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标准。我们总是无意识地把自己拥有的东西与他人拥有的东西相比较,这些“他人”包括我们的朋友、邻居,甚至还包括杂志上那对养眼的夫妇。而且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大脑默默计算得出的结论:与那个东西相比,这个远远不够。
这种“差异”是社会比较程度上升的信号。最常见的是,这种偏见是我们对周围客观世界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自己头脑中想象。我家的厨房灶台看着很低端,我的衣橱看起来老掉牙了。其实这些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变了。对它们不够好的主观感觉有双重的诱人品质:它不仅驱动我们想要更多的东西,还能为支持这些欲望提供物证,以此赋予欲望正当性。为什么现在有如此多的人埋首支付各种账单?其主要原因是伪装成“我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社会比较,即便他们的收入情况良好。上升的社会比较是一种持续的压力,推动我们走向自己能承受的最远边界。
事实上,我们能够对自己应如何进行比较施加更多的控制。受到控制的比较意味着:第一,学着认识我们什么时候受与他人比较的控制;第二,明智地选择何种比较才是真正相关和有用的。这个理念并不是要人停止比较;而是要大家更加明智地比较。
不同种类的比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向上攀比让我们感到自己更加穷困,更没才华,过得也更艰苦。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管理这些向上攀比的感觉和欲望,那么你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定向为一种向下的比较。我建议你想想那些没你幸运的人,通过跟他们比较,能让你感觉好一点吗?虽然看上去有点幸灾乐祸,但我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向下比较不仅是幸灾乐祸和自以为是的骄傲根源,它还是感恩之心的源泉。关键是你要意识到,如果你处于另一种情形之下,或是经历一次突如其来的财产变故,都可能导致你不如现在这般幸运。
向上攀比和向下比较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向下比较的危险是自满:当你开始感觉自己比其他人要好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不那么努力了。相反,向上攀比可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多的东西,但是这种攀比只有当我们确信自己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时候才能起到合理的推动作用。如果你自不量力地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迈克尔·乔丹相比,那么这种攀比只会让你自惭形秽,丧失前进的动力。
如果想要成功地在这两种比较之间达到平衡,那么你需要让自己的目标变得十分清晰。举个例子,你是否渴望提升自己的教育程度,或者是在事业中获得自我肯定?在这些情况下,选择向上攀比也许是有利的,但不仅仅是与那些富有或成功的人攀比,而是与那些在你感兴趣的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攀比。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已经满足或者超过了基本需求,但仍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那部分人,那么向下比较也许会给你提供一种健康的再校准模式。
我的妻子在把向下比较的理念付诸实践上很有一套方法。无论何时,她发现自己在抱怨某事时,她的大脑立刻就会调频到最坏的那种情况,而且她会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抱有感恩之心。譬如她的脚受伤了,那么她的下一个念头就是:“谢天谢地!我的脚还在!”她并不是觉得自己比世界上那些没有脚的人更优越,而是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提醒自己,她的脚是受到保佑的,她的处境本来有可能更糟糕。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拿自己与胜利者或失败者做比较,而是如何清醒地比较。展开向上或向下的比较是一种在我们的经历上加上下限的方式。那些上限和下限提供了理性的框架和视野,提醒我们自己的境况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虽然环境允许你与事情本身的样子和平相处,但如果你正在面对一个重大挑战,它也需要你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沉浸于一些向上的比较之中。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其他人的情况和你本人的过去重新为自己的选择定向。如果你已经克服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把现在的你与过去的你进行比较,无论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都会有帮助。你会从向下的比较中获得好处(“至少我不再是那个愚笨的少年了!”)并了解自己向上的轨迹(“看看这个世界吧,我来了!”)
因为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进行社会比较,那么另外一种管理不平等的效果的方法是改变所谓的“环境”。因此,除了改变自己的比较方式之外,你可以明智地选择你所处的环境。
10个美国人中差不多有4个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小镇。 [10] 另外20%的美国人虽然换了生活的城镇,但还是留在自己家乡的那个州。迁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这些迁移者的收入比留在镇上的人的平均收入更高,接受的教育层次也更高。离开或留在自己的家乡都涉及一系列妥协,并没有适合每个人的正确答案。如果你有办法从一个高度贫困的地区搬走,那么这永远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但是,抓住那些机会意味着以牺牲熟悉的社会准则和文化价值观为代价,还意味着你将抛弃一个能为你提供许多实际支持的大家族。
当然,并不是所有重大的迁移都需要离开你的家庭和朋友。但现实情况是,即便你只是从一个社区搬到同一地区的另一个社区,都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开展的大规模随机实验显示,把一个家庭搬离高度贫困的社区会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显著变化。 [11] 一组被随机选出的家庭能够得到住房补贴凭证,通过这笔租金补贴,这些家庭得以搬离此地;控制组的家庭同样得到了一笔租金福利,但是他们没有搬走。这笔福利的数目不大,因此这些搬离贫困社区的家庭实际上只是搬到了另外一些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而已。尽管如此,结果还是令人震惊。搬离贫困社区的家庭中,孩子变成单身父/母亲的概率更小,而在学校上学并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在他们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比那些留在旧社区的孩子的收入要多31%。
类似状况也表现在另一项研究中,该研究的对象是芝加哥拆除一些低收入住房项目。 [12] 芝加哥向这些低收入住房项目的居民提供住房补贴,让他们搬到贫困集中度不太高的地区。与住在其他住房项目里的租户相比,那些搬迁了的人有着更高的就业率,薪水也更高。在这两项研究中,搬迁的好处更加明显地体现在那些搬迁时还是孩子的人身上。这说明流动性主要是靠创造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家庭来改善其生活状况,最终惠及下一代。
迁移到更富裕社区的替代策略是搬迁到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方定居。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每个州、县的不平等数据及其邮政编码。不平等程度低的社区能够为居民提供福利,而且居民子女的生活成本以及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太高。
以上讨论的这些策略的主要目标人群是那些感到自己正在挣扎或者已经被落下的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你是收入阶梯上前20%的那部分人,情况就又不一样了。从经济学上讲,近几十年不平等的扩大可能对你来说是件好事。但近期的研究表明,高度不平等也存在一些缺陷,尽管这些缺陷与某人的资产净值相比而言不是特别明显。
第一,有证据证明,高度不平等与高犯罪率、高压力相关的疾病风险和高度的政治极化相关。这些问题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包括富裕人群。这也许就是人们在更加平等的地方会更快乐的原因,甚至在调整了他们的个人收入之后,待在更平等的地方,人们的幸福感还是更高。
第二,富裕人士应该关心减少不平等的现象,这与实际成果的关系较小,而与你成为哪种人的关系更大。许多人相信,一旦自己发了财,就会停止奋斗,停止比较,也会对自己的成功感到自满。但很少有人能一直满意下去,高度不平等的环境让满意变得更难。有一项研究以每个州在谷歌上搜索频率最高的词条为依据,比较了这些州的不平等程度,发现与不平等关联最强的是关于奢侈品的搜索。 [13] 一个人所在州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他们寻求用昂贵的珠宝、汽车和装饰品展示自己财富的欲望就越强。然而,许多研究也发现,在奢侈品上的花费也没有增加他们的幸福感。 [14] 对于富人来说,如果说社会比较是一台跑步机,那么高度不平等就会使跑步机加速,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跟上。
高度不平等也以其他形式鼓励成功人士不慎重的行为。回想一下我们关于股票选择游戏的研究,以及勒纳随机把实验对象分为成功者或失败者的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发现,当人们在某些事情上成功时,立即就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甚至当他们的成就是由实验者随机决定的时候,“成功的”实验对象都会假设是自己的勤奋和天才带来了这些回报。
心理学家保罗·皮弗(Paul Piff)领衔的研究指出,这种自我赋予的权利感会带来不幸的结果。 [15]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在十字路口通过的车辆,记录这些车辆的品牌、款式和车况,同时记录了这些车辆截道人行横道的行人,以及截道那些同样有权上路开车的司机的频率。开着越贵的车的司机,截道他人的频率就越高。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把一碗糖果放在等待区,并告诉实验对象,这是为另一项研究的孩子准备的糖果。他们发现那些把自己置于地位阶梯更高位置的实验对象吃这些糖果的概率更高。而另一项研究发现,收入更高的人把自己的收入捐给慈善团体的比例也更少,而这种差异在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州会被放大。
一旦有人对富裕人士提到他们可能拥有的一些优势和特权时,富裕人士通常会即刻做出反应:“我工作很努力,因此我值得拥有成功!”诚然,我认识的每一位成功人士都很努力,但是他们同样也得益于好运气和他人的帮助。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曾利用电脑模拟考查能力、努力和机遇在通往成功中所起的作用。 [16] 这个电脑模拟研究预假设98%的成功可以用能力和努力来解释,而只有2%的成功能用机遇来解释。在这些假设下,模拟中的大部分“胜出者”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都很高,跟你我的预期差不多。但是在模拟的“市场”中竞争变强的时候,一些与直觉相反的事情就会发生。当竞争水平达到最高时,每个人都会有很高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而在这种精英阶层中,把“特别成功者”从“一般成功者”中区分开的因素就是机遇。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富人不配拥有自己的收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取决于其能力、努力和机遇。但是,正如这个模拟研究强调的那样,你在梯子上爬得越高,你的成功就越受能力和努力以外的机遇所影响。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好运气和坏运气,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战胜成功带来的自我权利感。它也会帮助我们打消这种欠考虑的假设:世界永远是公平的,好人会有好报,恶人总会受到惩罚。就像我认为把向上攀比和向下比较放在一起能提供一种有用的语境,把我们的自然天性对自身优点和运气的关注放在一起也是如此。下次当你想到自己工作那么努力,也值得拥有你得到的那些东西时,不妨问问你自己,你这一路走来有多幸运。
如果你是成功且富裕的,那么你就处于一种特权地位并产生作用。你有更多的钱用于捐款,或者出于慈善或是政治原因促进平等。如果你是雇主,你就有能力以鼓励组织合作的方式设定工资范围,而非破坏组织合作。一些企业家已经做出了此类尝试。
一家信用卡服务公司的CEO丹·普莱斯(Dan Price)阅读了我此前描述过的研究报告, [17] 这份报告显示,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递增而上升,直到一个高点后,更多的薪酬则会导致幸福感的递减。基于这一研究,丹决定在2015年把自己公司的最低工资提升到7万美元。为了保证这个计划成功实现,他把自己的工资从100多万美元也降到了7万美元。两名公司高管的辞职证实了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即便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他们也认为付给入门级的员工那么多工资是不公平的。但是丹的大多数雇员都留了下来。人事变更率下降可能节省了公司在招人和培训新员工上花的钱。而且普莱斯断定员工士气和忠诚度的提升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时间会证明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还是蒸蒸日上。员工们非常感激,以至于他们最近集资购买一辆特斯拉送给普莱斯。
我最后一个想强调的策略不仅能够应用于贫困之时,还能应用于繁荣之时。这个策略在表面上看起来与社会比较、收入分配或社区环境毫不相关。但它在评估什么对你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件事上十分有用。我在这本书开头时曾提到,当我要求人们写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和动机时,几个同样的价值观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但没有人回答,是这些“价值观”塑造了“地位”。
如果你肯花点时间考虑一下你所珍视的价值观。你就有可能想出一个几乎其他所有人都同样珍视的价值观。你很有可能集中于一种个人的价值观,它把你同自己钟爱的事物,或者是一个大于你个体本身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这种价值观有可能与攀登社会阶梯毫无关系。
研究显示,这个集中于“什么最重要”的简单练习会对不平等的体验产生显著效果。 [18] 首先,它让人们不那么关心其他人的看法。在一个实验中,大学生被要求花几分钟写下对自己很重要的一种价值观。在一系列价值观和品质的列表(譬如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艺术技巧,创造力等)中选择一项之后,他们接下来被要求写几段话陈述一下这个价值观之所以对他们重要的理由,以及描述一个这个价值观曾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刻。控制组的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个其他人可能会关注的价值观,但是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参与者需要陈述他们为一个奢侈品手表或一个非奢侈品手表埋单的意愿有多强。写下对个人重要的价值观的那一组参与者对奢侈品手表的兴趣明显低于控制组。在另一项研究中,花了几分钟写一个关键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在被其他人评估时,则表现出了较低的心理压力。
心理学家布兰登·舒梅切尔(Brandon Schmeichel)和凯瑟琳·福斯(Kathleen Vohs)发现,花几分钟写珍视的价值观同样使人们不那么冲动了, [19] 也更可能将即刻的满足让位于长远的利益。这些研究说明,人们重新定位其真正关心的事物可以舒缓不平等引起的“快生早死”心态。
在迄今为止有关价值观的研究中,最有野心的当属心理学家戈弗雷·科恩(Geoffrey Cohen)与其同事利用价值观的力量与横亘在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收入鸿沟斗争。 [20] 他们创造了一种干预方式——在一学年的课程中进行几段短的写作练习。在实验组中,每项写作任务都包括描写一个对你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控制组中的学生同样需要完成写作练习,但写的是对其他人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当研究人员在年底检查学生的平均分时,控制组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GPA有着显著的差距,但在“重要价值观组”中,这个差距被降低了40%。
这个发现并不反常。科恩的团队用另外一个班的学生重复做了这个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当研究人员两年后再回来时,价值观组的学生一直把他们的上佳表现保持到了九年级。而科恩和心理学家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领导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白人学生和拉丁裔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这种缩小持续了为期三年的整个随访期。
在这个主题的另一个版本中,心理学家克里斯特尔·霍尔(Crystal Hall)访问了新泽西城内的一处流动厨房,与在那里用餐的人们交谈。她要求一组参与者对他们觉得很成功且自豪的经历说上几分钟。她要求控制组的成员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霍尔为两组人都提供了他们有资格申请的全部社会福利。为穷人提供福利的一个长期问题是,许多人没有申请能够帮助他们的福利项目,只是因为申请过程看起来很难,或是令人迷惑。即便他们可能知道申请这个福利与他们的长远利益相关,但还是经常对做此类事情感到有压力,这是短视思维导致贫穷的另一个例子。这个研究发现,对自己成功的有控制力的经历做5分钟的讲述,明显增强了他们申请福利项目的意愿。
这些惊人有效的干预并不需要上千万资金的支持去解码人类基因图谱,或者解开大脑的秘密。它们只需要几分钟的持续注意,这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是一种视角的简单转换——从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转换到一个更加现实的心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们习惯性地以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为背景衡量自己所处的相对地位,以图判断自己的价值。有意地考虑真正重要的事情会打断无意识的默认模式,即寻找其他人来衡量我们对自己的重视程度。
正在发展中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型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为何人性会与地位阶梯深深交织在一起。这是人的本性,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它与富人的私人喷气式飞机和赤贫者在垃圾场边上的谷仓有关,跟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我们也有关。把富人考虑劳力士腕表的价值和站在午餐档口前身无分文的四年级学生联系在一起,也是人的本性。对于人类这样的生物,在不平等中蓬勃发展最终意味着重塑阶梯。到那时,理解不平等的行为科学就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垂直化的世界中过得更安宁。
[1] D.Kahneman and A.Deaton,“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7(2010):16489-93.
[2] R.A.Easterlin,“Does Money Buy Happiness?,”Public Interest 30(1973):3-10;R.A.Easterlin,L.A.McVey,M.Switek,O.Sawangfa,and J.S.Zweig,“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2010):22463-68.
[3] S.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New York:Viking,2011).
[4] S.Oishi,S.Kesebir,and E.Diener,“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011):1095-1100.
[5] A.Ferriman,“BMJ Readers Choose the‘Sanitary Revolution'as Greatest Medical Advance Since 1840,”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4(2007):111.
[6] B.Mohan,M.I.Norton,and R.Deshpande,“Paying Up for Fair Pay:Consumers Prefer Firms with Lower CEO-to-Worker Pay Ratio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arketing Unit Working Paper(15-091),2015.
[7] N.Gordon,“The Conservative Case for a Guaranteed Basic Income,”The Atlantic,August 6,2014,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8/why-arent-reformicons-pushing-a-guaranteed-basic-income/375600/.
[8] A.Krue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presentation made to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anuary 12,2012,www.americanprogress.org/events/2012/01/12/17181/the-rise-and-consequences-of-inequality.
[9] J.Suls,R.Martin,and L.Wheeler,“Social Comparison:Why,with Whom,and with What Effect?,”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2002):159-63.
[01] 这里的弗洛伊德指的是肯塔基州一名叫弗洛伊德·柯林斯的青年。肯塔基州是一个洞穴众多但土地贫瘠的地方,当地人为了生计把一些洞穴包装成观光旅游地。1925年1月29日,当弗洛伊德在父亲的农场上探寻一个能够吸引游客的大洞穴时,不幸陷入困境,不能自救。人们想尽办法施以援手,还是不能把柯林斯从困境中解救出来,19天以后,饱受折磨的柯林斯悲惨地死在了洞穴中。美国记者威廉·伯克·米勒(William Burke Miller)将此情景拍摄成名为《在坟墓中的旅行》的照片,在1926年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10] D.Cohn and R.Morin,“American Mobility:Who Moves?Who Stays Put?Where's Home?,”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17,2008,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11] R.Chetty,N.Hendren,and L.F.Katz,“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2016):855-902.
[12] J.E.Rosenbaum and S.DeLuca,“What Kinds of Neighborhoods Change Lives:The Chicago Gautreaux Housing Program and Recent Mobility Programs,”Indiana Law Review 41(2008):653.62.
[13] L.Walasek and G.D.Brown,“Income Inequality and Status Seeking:Searching for Positional Goods in Unequal US Stat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6(2015):527-33.
[14] R.H.Frank,Luxury Fever:Why Money Fails to Satisfy in an Era ofExces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1);E.Dunn and M.Norton,Happy Money:The Science ofHappier Spending(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14).
[15] P.K.Piff,D.M.Stancato,S.Côté,R.Mendoza-Denton,and D.Keltner,“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109(2012):4086-91.
[16] R.H.Frank,Success and Luck:Good Fortune and the Myth ofMerit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17] P.Davidson,“Does a$70,000 Minimum Wage Work?,”USA Today,May 26,2016,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16/05/26/does-70000-minimum-wage-work/84913242/.
[18] N.Sivanathan and N.C.Pettit,“Protecting the Self Through Consumption:Status Goods as Affirmational Commoditi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2010):564-70.
[19] B.J.Schmeichel and K.Vohs,“Self-Affirmation and Self-Control:Affirming Core Values Counteracts Ego Depletion,”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2009):770.
[20] G.M.Walton and G.L.Cohen,“A Brief Social-Belonging Intervention Improves Academic and Health Outcomes of Minority Students,”Science 331(2011):1447-51;G.L.Cohen,J.Garcia,V.Purdie-Vaughns,N.Apfel,and P.Brzustoski,“Recursive Processes in Self-Affirmation:Intervening to Close the Minority Achievement Gap,”Science 324(2009):400-403;D.K.Sherman et al.,“Deflecting the Trajectory and Changing the Narrative:How Self-Affirmation Affec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Under Identity Threat,”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2013):591-618;C.C.Hall,J.Zhao,and E.Shafir,“Self-Affirmation Among the Poor: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Implications,”Psychological Science 25(2014):619-25.
本书之所以能问世,源于我的妻子——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要我停止抽象的探讨,描写我自己对不平等的经历和认识。我欠她一声道谢,不仅是因为她的智慧和对每章内容的深度评论,而且,在我旷日持久的“写作日”中,她还替我收拾各种烂摊子。我的家庭在这些书页中也有所体现,我尤其感谢我的哥哥杰森和我的父母——宝拉和米切尔,他们对我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大度。而我在书中提到的所有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有赖于我现在的学生和往届学生的辛勤工作与智慧,尤其是Jazmin Brown-Iannuzzi、Heidi Vuletich、Kristjen Lundberg、Erin Cooley、Daryl Cameron、Kent Lee和Jason Hannay。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Sam Fillenbaum阅读了这些章节,并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科学、著作和生活方面的建议。我无可匹敌的经纪人——理查德·派因(Richard Pine)在我对这本书只有一个模糊设想的时候,就始终抱有乐观和恒心,帮助我把它变成现实。还有我的天才编辑李克·科特(Rick Kot),他以稳准的手眼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变得更加精彩。我同样感谢米奇·普林斯坦(Mitch Prinstein)对注释的编辑,以及对我第一次写书过程中的起起伏伏的包容与怜悯。我想我们做到了。
近些年来,大家的朋友圈几乎每个月都会“焦虑”好几次,“逃离”好几次。《月薪三万还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这类问题在国内讨论得很热烈,除了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还有“原生家庭”“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等,其传播路径多为“由红转黑”,先是有一大批认为自己爬不上梯子的人们迎合转发,再有不少鸡汤文章反水,指责这些人故作矫情,实则内心幼稚,推卸责任,说的吐槽之人心里也发毛。这把“破梯子”到底存在不存在,写手与看客其实都没底。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本质都属于“发展型问题”而非“生存型问题”,无冻馁之患的人们陷入了现代性的焦虑之中。然而,社会心理频繁为此搅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此热议的也不仅是中国一国,作为现代性的附属品,由贫富差距带来的物质和心理病征同样席卷了东亚、美国和欧洲。在朋友圈刷屏文中,我们能举出无数的个案来证明它的存在,而作为一个“焦虑的新中产”,我关注的却是该问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遍程度如何,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与脑神经学博士基思·佩恩(Keith Payne)撰写的这本书的翻译任务。这本书中包含了他本人及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而更多的是对相关研究的系统爬梳和逻辑重整,更像是一本语言通俗的研究综述和科普著作。他综合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诸多研究成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攀比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如何影响生死的。
佩恩在第一章中就给出了“月薪三万妈妈”焦虑的深层理由——是“感觉贫困”而非“事实贫困”让人们感到受伤,人们判断“足够”的唯一标准就是通过与周围人的比较。其实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多鸡汤文章立足于此,教你“强大自我”,对这些差距“淡然处之”。但当“别人家的孩子”去常青藤游学时,你就忍心让自家孩子去北戴河的夏令营吗?佩恩所举的实验证明,这种“攀比心”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是人类甚至动物的本能,就连作为实验对象的猴子,在看到别的猴子吃到葡萄而自己只能得到黄瓜时,也会愤怒地将黄瓜扔到研究者的脸上。从佩恩所列举的研究来看,不平等不仅是影响人们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它甚至能在结构上改变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月薪三万妈妈”和“北上广徘徊者”并非只是矫情作态,佩恩的这本书为他们的焦虑提供了存在的正当理由。
无论你是否接受“原生家庭论”“阶层固化论”,实验数据都表明,处于相对弱势境况的人们理性程度更低,他们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宗教信仰的程度也较高。一项1991年的研究显示,在艰苦的、充满压力或无秩序的环境中长大的女性会更早生孩子——相对地位较低、更加贫穷的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快生早死”(live fast,die young)的生活方式,决策更加短视,更容易为了眼前利益去牺牲长远利益。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佩恩确认了不平等在“阶层固化”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的确加速了处于相对低位的人们劣势的循环,因此,处于阶梯底端的人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佩恩引用物理学的概念,把这种循环的力量称为“地心引力”,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人们会被无数负面因素自我强化,这让任何想摆脱这种引力的行为变得难上加难,只有努力达到“逃逸速度”的人们才能永远地摆脱这个恶性循环的困扰,无疑是凤毛麟角。因此,对“穷人本身有问题”的指控是缺乏同情心的,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不平等还在相当程度上划分着人们的政治观点,它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经济学问题,或是某个阶层、某些人群的伤春悲秋、忸怩作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关乎社会分配方式的伦理学问题。我们以上所提到的种种现象,都是这种日益拉大的不平等鸿沟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它背后隐藏着社会正义的问题,即社会基本结构的问题。很显然,如今在倡导“自由”的民主社会,罗尔斯提出的“平等的自由”都是天方夜谭,而若无“平等之自由”,又何来“公平之正义”呢?在此意义上,佩恩的这本书以充分的研究案例和统计结果,甚至是自己和家人的现身说法,将“攀比不平等”这一社会心理的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较为客观、全面、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是它作为一部学者专著与情绪性网络文字的差异。它是通俗的,同时也是严肃的。
作为腾讯网文化频道的学术编辑,我对自己有机会翻译这本“严肃的小书”而感到非常荣幸。本人是一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英文爱好者”,这也是我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有一句行话:“校书如秋风扫叶,旋扫旋生。”意为校勘过程中,无论你如何尽心竭力,总有错漏之处未入眼,更何况非母语的翻译工作,尤其是本人这种翻译新手,虽三校其稿,马虎的错误若无,未察觉的错误总有。在此,我要向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曲心如(Marina Chu)小姐表示感谢,她是著名社会学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先生的外甥女,不仅有着良好的社会学家学传统,还精通中、英、法三国语言,给了我很大帮助。同时,也对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的吴素萍主编、孟凡玲编辑表示感谢,正是她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以及后期专业细致的工作,让这本书得以此面貌出版。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母亲,他们作为我的译稿的“第一读者”,指出了许多我在翻译时“当局者迷”的问题;而我翻译本书时恰值孕期,他们对我身体和心灵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在情绪和精力都处于敏感时期的我得以如期顺利完成译稿。最后,我将自己第一部译著送给我的孩子,当这本书问世时,他/她应该已经先“问世”了,希望他/她今后在阅读这本小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十月怀胎的妈妈每晚在灯下伏案工作的心境,为他/她今后的人生提供一点前进的动力吧!
2017年10月17日夜
李大白

献给米拉
1957年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当时纽瓦克还很繁华,有标志性的百货商场、早报晚报、图书馆、博物馆、热闹的市中心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我的父母都在市区的意大利人聚集区出生长大,直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还住在那里的支溪公园附近。我父亲七年级时辍学去工厂上班,他的工友有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几场重大战役,除了服兵役的这段时间外,他一生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从普通工人做到工头,后来又当了工厂经理。
我的父母和其他千百万的美国人一样,在我开始蹒跚学步时决定搬家到郊区离纽瓦克15分钟车程的北阿灵顿小镇。他们经常提醒我,搬到这里主要是因为有好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平女王高中。他们坚信我和弟弟上了这所学校就能考上大学,从此前途一片光明。我姨妈朗妮一家当时已经住在那个小镇了,我姨夫沃尔特在纽瓦克工程学院获得了化学工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成了高露洁-棕榄公司的高级总裁。尽管我们一家属于蓝领家庭,而姨妈一家属于富裕家庭,但是我们能在同一个社区毗邻而居,可以说都属于同一个美国梦。我们搬离纽瓦克后,还能在周末回到原来的街区看望祖母和其他亲戚,一起享受美好的意大利晚餐。
1967年7月,9岁的我目睹了一次城市暴乱。当父亲开车带我们进城时,空气中充满烟雾,浑浊不堪:纽瓦克陷入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暴乱。警察、国家警卫和军事装备排在街道两旁,后来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警告我们有“狙击手”。我父亲一边紧张地给车子掉头,一边指导我们趴下以确保安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纽瓦克有几十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黑人,还有超过750人受伤,1000多人进了监狱,财产损失多达数百万。这场灾难性的暴乱蔓延到其他数个城市,包括附近的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普兰菲尔德,“铁锈地带” [01] 上的底特律和辛辛那提,以及南方的亚特兰大。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1967年漫长炎热的夏天”。在多数暴乱事件中,导火索都是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工作机会、经济活力以及以白人为主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开了城市,而在“大迁徙”中从南方搬来的黑人涌入城市,挤在市区的贫民窟里。 [1]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见证了后来被称为“城市危机”的问题的演变。以前我一直认为,在整个现代历史中,城市是工业、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的中心,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情况变了。中产阶级群体和工作机会都从纽瓦克等城市流向郊区,城市的经济被掏空了。7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纽瓦克成了经济衰退、犯罪率和暴力事件攀升及种族集中贫困的牺牲品。1975年我高中毕业时,纽约市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不久之后,我父亲的工厂也倒闭了,数百个和他一样的工人都失业了。希望、繁荣和美国梦都流向了郊区。
这些赤裸裸的现实常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什么人、公司和商店都离开了纽瓦克?为什么城市会爆发种族骚乱并迅速衰落?为什么我父亲的工厂会倒闭?早年间见证的那场最初的“城市危机”对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75年秋天我进入了罗格斯大学,有关城市及相关的种族、贫困、城市衰落和工业萧条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我。大二时,我的城市地理学教授罗伯特·莱克布置了一项作业,让我们游览曼哈顿下城并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我被当时纽约苏荷区(位于曼哈顿岛第二区)、东村和附近区域上演的奇妙景象惊呆了:社区充满活力,充满令人着迷的画家、音乐人、设计师和作家,旧仓库和工厂被改造成工作室和居住空间,朋克音乐、新浪潮音乐和嘻哈乐给酒吧等演出场所注入了激情。后来这一系列的萌芽演变为一场彻底的城市复兴。
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书的近20年时间里,我开始整理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匹兹堡曾饱受去工业化的困扰,流失了几十万人口和大量高薪蓝领就业岗位。所幸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医疗中心、企业研发部门和慈善事业,这个城市才没变得更糟。当时市政府努力想办法扭转乾坤,我作为经济发展学教授也参与其中。然而即便是前沿的研究创新潜力也没能留住匹兹堡的大学人才,我身边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学生都成批地前往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等高科技中心。当起家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互联网先锋Lycos(搜索引擎)公司也突然宣布从匹兹堡搬到波士顿时,我灵光一现。
传统观念认为,人才随着企业和工作岗位流动,在我看来这一观念已经过时了。匹兹堡的市政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减免税收等刺激政策来吸引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工业园区和办公园区,但这些并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也不是我的学生和其他离开匹兹堡的人才真正需要的。波士顿没有给Lycos提供任何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政策,实际上,在波士顿,从租金到员工工资的所有经营成本都远高于匹兹堡。Lycos迁址是因为,它需要的人才已经聚集在波士顿了。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断言,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企业。由知识工人、技术专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构成的创意阶层聚集在有以下特征的地方:有大量高薪工作——也被称作密集的劳动力市场;有大量可以结识和约会的同伴——我把它称为密集的同伴市场;富有生机,有大量餐厅、咖啡馆、音乐表演和其他娱乐活动。 [2]
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创意阶层群体已经增长到4000万人了,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3。我指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优势和主导阶层,他们的品位爱好不仅重塑着城市,还影响着文化、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同样指出了两个构成劳动力剩余部分的弱势阶层:一个是人数更多、工资更低廉的服务业阶层,有大约6000万人,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一半,他们从事低薪的食品制备、零售和个人服务工作;另一个是正在收缩的蓝领工人阶层,他们从事制造、建筑、技工、交通和物流工作,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5。
我进一步指出,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和都会区都在“3T要素”方面表现出色,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它们拥有密集的科技公司,拥有能提供人才的优质学校和研究性大学,还富有包容性,这使它们能吸引和留住不同性别、国籍、种族和性取向的人才。
城市就是把3T集合在一起的地方,并由此成为最基础的经济组织单位。在旧工业经济中,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为广泛的中产阶级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这个阶层既包括像我父亲那样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像我姨夫那样的白领管理层和工程师群体。地点本身已经变成了新型知识密集经济的中心组织单位,也是吸引人才、匹配人和工作岗位、激发创新和经济成长的主要平台。
我把这个理念带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治理者,尤其是那些仍相信老一套城市政策——如税收减免等刺激政策、修建市中心体育场馆和露天购物中心等大型设施——能吸引居民的城市官员。我告诉他们,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型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关键是要建造一些小型设施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比如建造人行道、适宜步行的街道、自行车道、公园、艺术场馆、演出场地,以及有咖啡店和餐厅、能吸引人流的活力街区。城市不仅需要竞争的商业氛围,更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形形色色的居民,不论他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或性取向如何。
我的观点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包括市长、文艺界领袖、城市规划专家,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想找到促进城市发展得更好的方式。我的主张也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强烈反对。有些保守派质疑我把多样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观点,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和就业,不是创意阶层。有些人(主要来自左派)把房租上涨、中产阶级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账都算在创意阶层和我个人头上。还有一些更个人层面的批评,虽然令人不快,但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考,使我开始重塑对城市和影响城市发展因素的看法。
我对城市的理解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过于乐观地相信城市和创意阶层会自动带来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强劲复苏的城市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迅速扩大了。随着科技从业者、专业人士和富人搬回城市,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以及部分艺术家、音乐人都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挤出了城市。在纽约苏荷区,我在学生时代看到的促进艺术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元素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富人群体、高级餐厅和奢侈品商店。
老实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城市复苏的弊端。早在2003年(那时让大家开始关注“前百分之一”群体崛起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还未发生,提出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还未问世),我就提出警告:美国最富创意的城市同时也是经济不平等的中心。我的研究表明,薪酬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大都市恰恰是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如旧金山、奥斯汀、波士顿、西雅图、华盛顿和纽约。 [3] 虽然当时我记录下了这些新出现的分裂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扩散速度会有多快,也不知道这些城市的两极分化问题会有多严峻。仅仅过了10多年,我曾预言的城市复兴就带来了广泛的绅士化,房价变得难以承受,富有的新市民和艰难维生的老市民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我最担忧的是大量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这些社区曾是城市和社会的支柱。它们是我在纽瓦克出生的地方,是我在北阿灵顿生长的地方,也是我曾希望新创意阶层能带回城市的社区。但现在,这些强大的中产阶级社区正在我眼前消失。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知识重构,写作了本书。我看到了自己以前大力歌颂的城市复兴运动的黑暗面:重返城市运动把绝大多数的好处都分配给了少数的地区和人群。
分裂扩大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仔细分析,我发现只有少数城市和都会区真正通过知识密集型经济实现了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跟上,而是越落越远。很多“铁锈地带”上的城市仍在人口向郊区迁徙、城区衰败和去工业化的泥潭中挣扎。“太阳地带” [02] 上的城市仍在用低廉房价、郊区散漫无序的扩张发展吸引人才,但很少能建立起知识创新驱动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数千万美国人仍陷于长期贫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分裂问题。随着中产阶级群体和社区的消失,城市版图被割裂成少数的富人及优势群体聚集区和多数的穷人及弱势群体聚集区。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城市化不平等的正是人才和经济资源的聚集,只有少数超级城市和精英社区从城市化中获利,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远远滞后或停滞不前。这股推动城市经济广泛发展的力量也带来了分裂和矛盾,阻碍城市继续发展。
最终,我的研究使我不得不面对令人忧心的城市新版图。常识和经济学研究都告诉我们,知识密集型大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经济状况更好。但我和我的同事通过研究三个阶层群体支付房租后的生活状况,意外地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现象:知识工人、专业人士和传媒文化产业从业者这些优势创意阶层过得还不错,能在大型知识密集型都市获得高报酬,并且所获报酬对负担这些地区的高住房成本绰绰有余。但另外两个较弱势的群体,即蓝领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就被远远甩在其后,支付住房费用后,他们实际上在消费昂贵的大都市过得更糟了。 [4]
这个现象背后的隐含信息深深地困扰着我。创新、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最强驱动力——人才和其他经济资源在城市的聚集把大多数利好都带给了原本的优势群体,而把剩余66%的人口落下了。我写下这些研究成果时引起了一阵小风波,一位批评家甚至宣称我已经承认了创意阶层理论的局限。我当时直接做了回应 [5] ,但我更完整和深入的回答正在你手中的这本书里。
我在第二故乡多伦多的所见所闻深刻影响了我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看法。2007年我搬到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研究城市繁荣问题的研究所担任主任。对我而言,多伦多是先进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拥有北美最多样化的人口、几乎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繁荣经济、安全的街道、优质的公立学校和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曾被彼得·乌斯蒂诺夫称作“瑞士人管理的纽约”的先进多元化城市选了罗布·福特当市长。
尽管福特的个人问题可能使他深受“福特王国”支持者们的钟爱,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反城市化的大城市领导人之一。当选后,他就立即着手拆除了几乎所有城市规划师眼中构成伟大城市的东西。他拆除了主干道两边的自行车道,以此恢复他的“汽车上的战争”,他还提出计划将市中心的主要湖畔地带变成带大型摩天轮的万众瞩目的购物商场。福特之所以能当上市长,大概正是因为他想将城市变得更像郊区。 [6]
福特上任是城市阶层不断分化的结果。多伦多曾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后来随着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缩减,社区逐渐消失,城市分裂成了少数小型的富人、知识分子社区和多数大型弱势群体社区。前者分布在市中心及附近主要地铁和火车线路周边,而后者则远离市中心和交通枢纽。 [7] 福特传递的信息在工人群体和新移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认为精英们占尽了城市复苏带来的好处,而他们则一无所获。
我认为不断扩大的阶层分裂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一个像多伦多这样进步、多元和繁荣的城市都可以沦为民粹主义集体抵制的牺牲品,那么其他城市更不能幸免。
那时我就提出,福特只是这场不断发酵的冲突的第一个信号,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如我所言,紧接着英国就决定脱离欧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尽管富裕、有全球性眼光的伦敦人强烈反对脱欧,但饱受全球化和再城市化双重折磨的工人阶层则普遍支持这一决定。
后来发生的事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更可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得益于他动员了美国较落后地区愤怒而焦虑的选民。虽然希拉里·克林顿拿下了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且知识集中型的城市及其近郊,并且这些新型经济中心确实帮她赢得了远远领先于特朗普的大众选票,但特朗普拿下了广大偏远郊区和农村,从而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朗普当选、福特上任和英国脱欧这三件事都反映了今天不断深化的阶级和地域断层。
政治分裂从根本上起源于“新城市危机”的深层经济与地理结构,是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的产物。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人才和优势群体聚集起来,占领了少数发达的超级城市,把其他人和城市甩在身后。“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更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危机。
在本书中,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呈现新城市危机以及城市和社会的深层矛盾。我有三个主要写作目标:阐述危机的主要特征;明确危机的根本成因;提出措施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城市化,即在鼓励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同时,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工作岗位、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更优质的生活方式。
如今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我们应对新城市危机的方式将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深分裂、持续倒退、陷入经济萧条,还是向前一步,迈向包容的可持续经济繁荣的新纪元。
[01] 铁锈地带,指美国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编者注
[1] 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报告(克纳委员会报告)(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Max Herman, Summer of Rag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67 Newark and Detroit Riots (Bern: Peter Lang, 2013); Kevin Mumford, Newark: A History of Race, Rights, and Riots in America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Sidney Fine, Violence in the Model City: The Cavanagh Administration, Race Relations, and the Detroit Riot of 196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Thomas J.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3]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ichard Florida, “The New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Monthly, March 2003; Richard Florida,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02] 太阳地带,美国南部到西南部,气候适宜,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编者注
[4] Richard Florida, “More Losers Than Winners in America’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CityLab, January 30, 2013, www.citylab.com/work/2013/01/more-losers-winners-americas-new-economic-geography/4465.
[5] Joel Kotkin, “Richard Florida Concedes the Limits of the Creative Class,”Daily Beast, March 20, 2013,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3/20/richard-florida-concedes-the-limits-of-the-creative-class.html; Richard Florida, “Did I Abandon My Creative Class Theory? Not So Fast,Joel Kotkin,” Daily Beast, March 21, 2013,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3/21/did-i-abandon-my-creative-class-theory-not-so-fast-joelkotkin.html.
[6] Richard Florida, “How Rob Ford’s Pride Snub Hurts the City of Toronto,” Toronto Star, April 23, 2012, www.thestar.com/opinion/editorialopinion/2012/04/23/how_rob_fords_pride_snub_hurts_the_city_of_toronto.html; Richard Florida, Toronto Needs a Muscular Mayor,”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30, 2012, 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richardflorida-toronto-needs-a-muscular-mayor/article5822048; Richard Florida,“What Toronto Needs Now: Richard Florida Offers a Manifesto for a New Model of Leadership,” Toronto Life, October 22, 2012, www.torontolife.com/informer/features/2012/10/22/what-toronto-needs-now. 也参见Zack Taylor, “Who Votes for a Mayor Like Rob Ford?,” The Conversation,November 13, 2013, http://theconversation.com/who-votes-for-a-mayorlike-rob-ford-20193; Zack Taylor, “Who Elected Rob Ford, and Why? 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2010 Toronto El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aterloo, Ontario, May 2011, www.cpsa-acsp.ca/papers-2011/Taylor.pdf。
[7] 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最早提出了这一现象,参见J. David Hulchanski,in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2005,” Cit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www.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curp/tnrn/Three-Cities-Within-Toronto2010-Final.pdf. 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No Longer One Toronto,” Globe and Mail, October 22, 2010, 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no-longer one-toronto/article4329894。
假设你能回到1975年的纽约,在大街上随机选一个路人,把他送到今天,他会怎样看待现在的纽约?在他所熟悉的纽约,经济急剧衰退,居民、企业和就业机会都在流向郊区,城市濒临破产。纽约是肮脏、危险和暴力的代名词。
如今,他应该还能轻易地分辨方向。布朗克斯区还在北边,炮台公园还在南边。自由女神仍俯瞰着曼哈顿的海港,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和林肯中心等地标建筑风采依旧。交通仍然同往年一样拥堵,他可以乘坐同样线路的地铁在曼哈顿市区穿梭,或是去布鲁克林、皇后区或布朗克斯区,也能乘纽新航港局过哈得孙河捷运去旁边的新泽西,再换乘新泽西公共地铁和大都会北方铁路去更远的郊区。
但很多其他事情都大不相同了。非常遗憾的是,在1975年还崭新的双子大楼现在已不复存在。重建后的金融区里除了商务人士之外,还搬来了很多以前住在郊区的富裕家庭。金融区附近以前是一片废墟,只有残砖废瓦和破败的码头,现在却建起了绿意盎然的公园,公园里延伸出贯穿整个曼哈顿哈得孙河沿线的自行车道。时代广场仍是一片霓虹灯和广告牌的海洋,但原来成人电影院和性用品店林立的地方变成了都市版的迪士尼,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户外桌椅供游客休息。以前的苏荷区挤满了非法搬入的艺术家,东村和西村的大街上则随处可见嬉皮士和朋克爱好者,现在这些地方则是各色高端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高薪投行人士、技术专家、游客甚至社会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肉类加工区的肉食处理工厂、仓库和隐蔽的同性恋酒吧现在也消失了。人们把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一个长长的公园,公园两侧是崭新的公寓和办公楼、惠特妮美术馆、精品酒店和高档商店。附近的纳贝斯克工厂变成了高端美食城,旧的港务局大楼现在挤满了谷歌的工程师,而谷歌只是这片社区里许许多多的科技公司之一。在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和哈得孙河对岸的霍博肯市和泽西市,原来只有大片的工厂、破旧的租屋和联排住宅,现在则是年轻职业人士和家庭聚集的社区,他们在这里居住、工作和娱乐,晚上也能在大街上散步,无须担心遇到抢劫犯罪事件。
然而,这个1975年的纽约人也能感受到,虽然今天的纽约看起来一应俱全、光鲜亮丽,但是某些问题正在内部发酵。对于他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在这里生活比1975年艰难多了。那时售价50000美元的公寓现在至少值上百万美元,而那时月租金500美元的公寓现在的租金至少要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他能看到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在57街拔地而起,那是亿万富豪们的住宅,但因无人居住而被闲置,在夜里往往一片漆黑。他还会听到人们抱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百分之一”人群崛起,以及令中产阶级越来越难以负担的城市高昂的物价。
除了财富新贵和游客外,他还能看见大量状况堪忧的社区紧挨着财富新贵们的社区。贫困、犯罪和毒品等社会问题以前阻碍着城市发展,而这些问题现在转移到了从前聚集着中产阶级社区的郊区。让他惊讶的是,民主党人士终于在2014年当上了纽约市市长,而在这之前的20年,纽约市市长的位置都被共和党占据,其中包括一位连任三个任期的超级富豪。让他更震惊的是,这位新上任的民主党市长以前是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社区积极分子,他的竞选理念就是改变纽约“双城记”的现状:穷人和富人就像生活在两个城市。“双城记”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个来自1975年的纽约人在过去的40多年中错过的事情。
我从出生以来就住在城里或城市周边郊区,并一直在仔细观察这些地区。我对城市规划进行学术研究已超过30年,见过城市衰落,也见过城市复苏,但这些都没有使我准备好面对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城市似乎正要走出困境,居民和就业都回到了城市,但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飙升等新问题又出现了。好像一夜之间,人们翘首以盼的城市复苏就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城市危机。
很多评论家都抓住了这场危机出现的原因,但鲜有人意识到它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前沿城市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城市化乐观派和城市化悲观派。虽然每个阵营都指出了城市化的部分事实,但双方各持一隅之说,无法帮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化危机,更无从帮我们找到解决之道。
城市化乐观派强调城市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城市化有益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 [1] 他们(包括不久前的我自己)认为,今天的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安全、干净和健全,城市化就是一切改善的源头。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政府减少干涉,让城市及其管理者有更多自主权,世界会变得更好。
与之相反,城市化悲观派认为今天的城市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超级富豪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富裕封闭区域,另一部分是周边普通民众生活的大片贫弱区域。他们认为,贪婪的资本家是城市复兴的始作俑者,资本家通过重建某些社区并摧毁其他社区大发横财。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秩序造成的,它的标志并不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是贫民窟和与之相伴相生的巨大的经济、生态和人道主义危机。 [2] 另外,绅士化和不平等就是富人和优势群体对城市再殖民的直接产物。
所以城市究竟是什么?是乐观派歌颂的伟大创新引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楷模,还是悲观派批评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分化之地?实际上两者皆是。城市既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也造成了恼人的社会分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矛盾。要理解现在的城市危机就必须认真对待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我尝试汲取了两者的精华。
“新城市危机”到底是什么?
过去5年我的所有研究都专注于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为此,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起就以下主题挖掘新的数据:城市不平等的范围与根源、经济隔离的程度、绅士化的成因与规模、全球超级富豪居住的城市与社区、初创科技公司聚集给城市带来的挑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对艺术与音乐创造活力的压抑。我把自己对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与城市社会学家关于集中贫困的腐蚀效用的见解结合起来,绘制了社区和阶层的分化地图,探索郊区贫困和经济危机的发展。我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它们很难通过城市化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 [3]
新城市危机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之间发生的旧城市危机。旧城市危机被定义为城市丧失经济职能、城市经济被架空的危机。由于去工业化和白人大迁移的影响,城市中心被逐步掏空,城市学家和城市管理者称之为“甜甜圈中间的洞”。由于核心产业的迁出,城市成了长期贫困聚集地:住宅区逐渐衰落;暴力犯罪事件攀升;毒品泛滥、青少年怀孕和婴儿夭折等社会问题激增;城市经济陷入衰退,税收不断减少,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经济资助。 [4] 这些问题大多延续至今,尚待解决。
但新城市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人们通常以为,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飙升等典型问题只存在于纽约、伦敦和旧金山等发达城市,其实“铁锈地带”城市和一些依靠能源、旅游业和地产业而没有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太阳地带”城市也饱受其害。新城市危机的其他主要问题,如经济和种族分化、空间不平等和长期贫困等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广泛存在于郊区。从这个角度看,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还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本身的危机以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我看来,新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少数超级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和巴黎)及高新科技与知识中心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华盛顿、波士顿和西雅图)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超级城市和地区坐拥全球绝大多数高价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初创公司和人才。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圣迭戈和伦敦这六个城市或地区吸引了全世界一半的高科技风险投资 [5] 。赢者通吃的城市化在不同城市之间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其他城市大多受到全球化、去工业化的冲击,丧失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超级城市的差距越发扩大。
第二是超级城市的成功给自身带来的危机。它们普遍面临房价高企且不断攀升以及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的问题。在这些城市,绅士化已经演变为一种“富豪统治主义” [6] ,超级富豪购置高端房产是为投资而非居住,社区变得死气沉沉,因此最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城市社区成了专供富豪彰显身份的工具。被迫离开城市的不仅仅有音乐人、画家等创意人群,越来越多经济条件良好的知识型工人也发现城市的高房价将耗尽他们所有的积蓄,他们还担心自己的后代可能再也买不起房子。但是直接承担经济后果的还是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者、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些人被赶出了超级城市,也享受不到超级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向上一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当教师、护士、医院工人、警察、消防员、餐厅服务生等服务人员都无力承担他们工作地点附近正常范围内房屋的居住成本时,城市的正常经济运转也难以为继。
第三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这方面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危害也更大,无论是“赢家”城市还是“输家”城市都难以幸免。如果说旧城市危机的特征是“甜甜圈中间的洞”,那么新城市危机的特征就是“消失的中层”——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曾作为美国梦实体化身的中产阶级社区都在不断减少。从1970—2012年,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65%下降到40%,而住在穷人社区和富人社区的家庭占比大幅上升。在过去的15年中,约90%美国都市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都出现了下滑。 [7] “穷城市、富郊区”的社会阶层划分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拼布城市”,即小片富人社区与大片贫困社区交织,同时存在于城市和郊区中。
第四是日趋恶化的郊区问题,如贫穷、攀升的犯罪率、愈演愈烈的财富分化和种族隔阂。情景喜剧《脱线家族》里那样的郊区中产阶级生活场景已经越来越少见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已经超过城市——郊区住着约1700万穷人,而城市里只有1350万。2000—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幅达到惊人的66%,而同期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幅只有29%。 [8] 郊区的贫困人口中少部分是从城市搬来的无家可归者,但大部分都是当地人。由于失业或者房价上涨,部分中产阶级陷入贫困,从原本的阶层跌落。以前郊区都是美国的富人区,但现在郊区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不逊于城市。
第五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乐观派相信,城市化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产阶级群体壮大,美国、欧洲、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都是发展这条道路的成功范例。毕竟从古至今,城市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如今,在许多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关联被割裂了,甚至出现了城市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涌入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显著提高。全世界还有超过8亿人口极度贫困,生活在条件堪忧的贫民窟,这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量的2.5倍,而且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 [9]
新城市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说到底是由城市人口聚集的悖论导致的。城市人口聚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实体企业、经济活动、人才和野心家在城市的聚集是现代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自然资源甚至是超大型公司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了,城市聚集人才的能力才是。当人才聚集起来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并形成合力,就能极大地提高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带来新发明和创业型企业,促进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中程度高得惊人:全球最大的50个城市人口总和只占全球人口的7%,却创造了全球40%的经济活动;全球40个超级都市群(例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经济长廊)只占全球人口的18%,却贡献了2/3的全球经济产出和超过85%的创新活动。如果单看一线城市的某些小型区域,经济聚集程度则更加惊人。例如,旧金山的市中心区域每年就能吸引数十亿风投资金,比除了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风投资金量都多。 [10]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而不是知识驱动型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人口聚类驱动发展,但它也使城市和社会产生严重分化。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聚集在同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一些东西必然会把另一些东西挤出去。这就是“城市土地关系”的本质,它是经济活动在少数城市里的小片区域的高度密集和对这些地区的激烈竞争的产物。 [11] 就像人生中多数事情一样,在对城市空间的竞争中,赢家往往是那些手里有最多可支配资金的人。富人和优势群体返回城市后占领了最好的地段,其他人只能被塞到那些不太好的城区或者郊区去。这种竞争导致了一种与之相关的经济悖论——土地悖论——世界上似乎有用不完的土地,但人们最需要的土地似乎永远不够多。
在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地域和阶层一起对社会经济的优势进行强化和再生产。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住在最好的社区,通过社区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服务和经济机会,而其他人只能住在他们挑剩的社区,获得所有资源的次级版本和更小的向上层阶级发展的可能性。富人住在少数优势城市的少数优质社区,为自己和后代赚到了远超其人口占比的大量经济资源。
不幸的是,在特朗普时代,这种分化只会被加深和固化。虽然特朗普大肆宣扬民粹主义的论调,号称要为被遗忘的蓝领工人阶层争取利益并重塑中产阶级,但特朗普政府和占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不可能改变导致分化的深层结构性力量,更不可能帮助那些掉队的人和地区。
新城市危机十分令人忧心,但我们能及时找到应对方案。虽然我对城市化的乐观程度有所保留,但我没有对城市化丧失信心。毕竟“危机”一词有两层含义,它既可以表示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危急形势,也可以表示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个节点,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
这就引出了本书最关键的部分:如果我们面对的危机在于城市,那么我们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即便城市制造了这一切的挑战和危机,但它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引擎。新城市危机的化解方案是城市化的发展而非倒退。
为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框架构筑更全面、更平等的城市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公路系统和住房建设的投资。这些公路和住房巩固了郊区发展,进而提振了居民对汽车、电视、洗衣机、烘干机和其他耐用品的需求,生产耐用品的工厂又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但现在郊区发展举步维艰,与驱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城市人口聚类越来越格格不入,我们需要一种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模式,我称之为“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一度乐观地认为民主党会赢得大选,组建的新政府会获得各大城市市长的普遍支持,并能持续提供我们实现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所必需的国家投资。不幸的是这一愿景落空了。我写到本书结尾时,不得不面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竞选的残酷现实,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国家财政对城市的投资将十分有限,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也将更少。虽然特朗普政府承诺要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优先级最高的很可能是公路和桥梁而不是运输。地方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慈善机构需要共同努力,弥补共和党的不作为,修补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安全网——现在受损严重的社会安全网对劣势人群和他们所在的社区有严重的不利影响。市长和当地官员应当刻不容缓地带头解决运输、经济适用房和贫困等城市问题。
最后,要走出困境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改革区划法规、建筑规范以及税收政策,让人口聚类的效应惠及所有人。
●加大基建投资,提高人口密度并强化聚类作用,限制昂贵且低效的城市无计划扩张。
●在城市中心地区建造更多廉租房。
●将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转换为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扩大中产阶级群体。
●通过对人和地区的投资解决集中贫困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构建更繁荣的城市。
●授权社区和当地官员发展本地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
本书的最后一章对上述内容还有更详尽的阐述。但首先,我想从系统和实证层面全面展示新城市危机的特征。第二章介绍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形成过程,详述“赢家”城市和“输家”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赢家”和“输家”对城市空间的竞争。第三章概述了新“精英城市”的崛起,以及它是如何让相对优势群体,即知识分子、科技专家和创意工作者竞争城市空间的。第四章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绅士化这一热点问题,调查它的发生地点和过程、部分居民被迫离开城市的问题,以及被城市化抛在身后的长期贫困地区的状况。
后几章侧重于重塑城市的阶级分化现象。第五章阐述城市和不平等现象的密切联系,解释为何不平等问题在大城市和普通城市的市中心地区更严重,以及为何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口聚类效应导致了不平等。第六章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调查中产阶级群体及其社区的衰落,研究美国围绕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产生的社会分化。第七章描绘了美国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各阶层人口分布变化情况,展示旧的“穷城市、富郊区”断层是如何让位于各阶级交错分布的新型“拼布城市”现象。
最后的三章分别着眼于城市外部、国外和未来。第八章研究不断深化的郊区危机。第九章探寻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没有带来实质发展的问题。最后的第十章展望未来,强调城市、国家和全球层面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并开创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新纪元。
[1] 城市化乐观派包括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 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卡兹和政治学家本粟明·巴伯。参见Edward Glaese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Healthier, and Happier (New York: Penguin, 2011); Bruce Katz and Jennifer Bradley, 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 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2] 城市化悲观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和城市学家迈克·戴维斯等。哈维写道,“这些新的发展无一不伴随着大规模人口的流离失所和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破坏,不仅造成了物质上的负面影响,还影响社会团结、扩大社会不公,把民主城市治理抛掷脑后,反而指望把军事化的警方监控和恐怖活动当作社会规则的主要模式。”参见David Harvey, “The Crisi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Post: Not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Around the Globe, Museum of Modern Art,November 18, 2014, http://post.at.moma.org/content_items/520-the-crisisof-planetary-urbanization;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2006)。
[3] 罗伯特·桑普森和帕特里克·夏基的著作给了我很多启发,参见Robert J.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本书也受到以下出自我的团队的研究的影响: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50, no. 1 (2014):1–14; 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Divided-City.pdf;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4] 20世纪70年代,罗格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把美国的市中心比作名副其实的“沙盒”,政府用联邦转移支付项目安抚这里的贫困少数族裔群体。参见George Sternlieb, “The City as Sandbox,” National Affairs, no. 25 (Fall 1971):14–21, 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_interest/detail/the-city-as-sandbox。
[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pdf.
[6] “富豪统治主义“一词引自Simon Kuper, “Priced Out of Paris,” Financial Times, June 14, 2013, www.ft.com/intl/cms/s/2/a096d1d0-d2ec-11e2-aac200144feab7de.html。
[7] 关于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衰落的问题,参见皮尤研究中心,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May 11, 2016,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有关1970年至2012年居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家庭数据,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9] “没有增长的城市化”的概念来自Remi Jedwab and Dietrich Vollrath,“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7 (July 2015): 1–94. 有关全球贫民窟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参见联合国人居署的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1143016_alt.pdf, 7. 也参见 联合国人居署,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6/05/WCR-%20Full-Report-2016.pdf。
[10] 超级都市群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im Gulden, “Global Metropolis: Assess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pril 2012, 178–187; Richard Florida, Tim Gulden,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3 (2008): 459–476. 风险投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Venture-Capital-GoesUrban.pdf;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The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 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pdf。
[11] 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在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London:Pion Press, 1980) 中最早提出了城市土地关系的概念。也参见Allen J.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no. 1 (2015): 1–15。
2013年秋天,游戏巨头美国艺电公司在时代广场的一个酒店套房发布了《模拟城市5:明日之城》,这是当时已风靡全球的《模拟城市》系列游戏的最新版本。与传统电脑游戏不同,在《模拟城市》系列里,玩家并不通过杀人赢取积分,而是以市长的身份管理城市。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税收、市区划分和土地使用规则等措施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还能点击屏幕上的市民,查看这些措施对于这个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模拟城市5:明日之城》设定的残酷未来世界里,一个叫控制网的精英集团控制着城市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市长可以限制这个集团的权力,但风险就是可能导致城市经济陷入停滞。发展太慢,城市就可能陷入贫困的反乌托邦境地;发展太快,城市的贫富差距会扩大,大量市民将无力负担高额生活成本而被迫离开城市。要赢得游戏,玩家就得在这两个不完美的选项之间寻求平衡。 [1]
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虽然游戏是虚拟的,但它描绘的基本矛盾正在现实世界中上演。
在城市聚合力的作用下,顶尖人才、野心家、富豪和最富创造活力的核心产业纷纷往超级城市和全球知识技术中心迁移,其聚集程度之高史无前例。 [2] 然而,在少数精英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数其余城市却在困境中挣扎、停滞不前,只能仰望后尘,这个过程就是“赢者通吃城市化”。
虽然这个名词是我创造的,但人们对赢者通吃经济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近20年前,罗伯特·H.弗兰克和菲利普·J.库克就提出了广为人知的“赢者通吃社会”的概念。他们参考的是经济学家舍温·罗森的研究成果,而舍温·罗森在他们之前的20多年就研究了超级明星崛起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普通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已经不低,但一流体坛明星和普通运动员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天上和地下。像勒布朗·詹姆斯、凯文·杜兰特和斯蒂芬·库里这种篮球明星,或是像汤姆·布雷迪和阿隆·罗杰斯这种橄榄球明星,收入水平都是普通运动员的数倍。同样,在娱乐圈,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和碧昂斯的收入是普通音乐人的数倍,影视巨星詹妮弗·劳伦斯、斯嘉丽·约翰逊、汤姆·克鲁斯、布莱德利·库珀和道恩·强森也是如此。背后的经济原理很浅显,超级歌星有大量粉丝愿意出高价买专辑和看演唱会;超级影星只要翻拍续集就能揽得高票房;体坛明星能吸引粉丝买比赛门票,去现场给他们助阵……这就是他们能获得超高报酬的原因。 [3]
但是弗兰克和库克发现,赢者通吃现象广泛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从咨询、银行和管理到设计、时尚、医药和法律等行业都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表现为首席执行官和普通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1978—2015年的近40年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增长率超过940%,而普通职工的收入增长率仅为10%。1965年,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职工的20倍,但到21世纪初,这个比例竟超过了300倍,此后一直维持这个倍数。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股票期权等股权报酬,其目的是激励管理者提升公司业绩。但事与愿违,实际上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之间联系甚微。一项针对429家公司的800名首席执行官的研究发现,从2004—2014年,首席执行官薪酬最高的公司反而整体运营情况最糟糕。 [4]
城市之间也开始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超级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样,轻松凌驾于普通城市之上。它们拥有最强的创新实力,控制着全球最大份额的资本和投资,并聚集了业界顶尖的金融、媒体、娱乐和高科技公司。因此,超级城市成了野心家和顶尖人才的必然选择。超级城市在持续不断地累积并强化自身活力:经济扩张刺激了对高级餐厅、剧院、夜店和画廊的需求;成功人士为城市捐助建设博物馆、音乐厅和学校;政府将不断增长的税收投资于学校、交通、图书馆和公园等公共设施,以此维持并强化城市自身的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这种强大的反馈循环使超级城市能不断积聚优势。 [5] 而欧美发达地区没落的老工业城市和发展中国家贫困闭塞的城市都远远落后,它们与超级城市的差距正不断扩大。
超级城市都有哪些呢?有很多版本的全球城市排名,各自侧重不同的考察指标,如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宜居性。为了集各家所长,我们用五项核心指标生成了“世界超级城市指数”。 [6] 我们先给城市进行单项排名,排名第一的城市10分,第二的城市9分,依此类推,然后把五项指标的得分加总,得到每个城市的总分。请注意,这些总分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值,是用来比较各城市相对优劣及划分梯队的参照物(见表2.1)。
表2.1 世界超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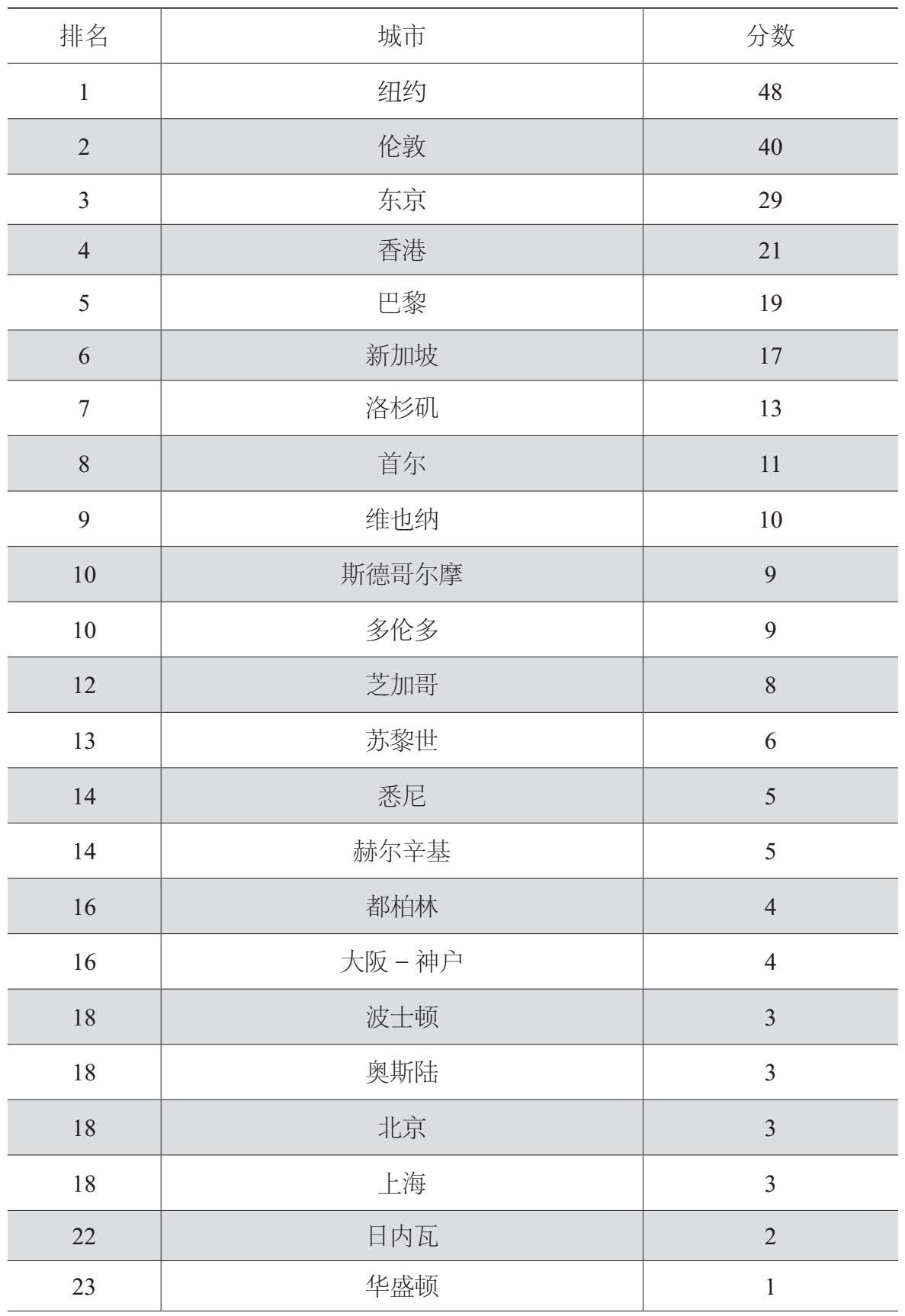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全球城市的五项核心指标。
纽约和伦敦分别以48和40的得分名列超级城市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包括得分位于13~29区间的东京、香港、巴黎、新加坡和洛杉矶;第三梯队包括首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多伦多、芝加哥、苏黎世、悉尼、赫尔辛基、都柏林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金融经济中心,以及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样的知识科技中心。超级城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度远高于它们和自己所在国其他城市的相似度。 [7]
超级城市独特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产业,如金融、媒体、娱乐和科技等行业。 [8] 在这里,一切都在高速运转——信息光速传播、创新层出不穷、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快速扩张,速度与规模一起构成了超级城市的生产力优势。快节奏不只是人们的主观印象,如俗话说的“纽约的一分钟” [01] ,而是客观的科学现象。在专门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圣菲研究所,科学家发现了城市的独特代谢方式:生物的体型越大,代谢率越慢;而与之相反的是,城市的面积越大,代谢率越快。圣菲研究所还提出,城市人口每翻一倍,居民的创造力、生产力和健康指数就平均提升15%。 [9]
超级城市的优势比超级明星更具持久性。名声再响亮的明星都会陨落,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较短,往往受伤后就退居二线,票房巨星会随着年华老去慢慢淡出舞台。有的大城市也会衰落,比如底特律,但超级城市只会越来越强。在过去不到20年中,纽约遭受了几场重大灾难:2001年的恐怖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12年的飓风“桑迪”,但它现在仍是全球最发达的城市。 [10]
在某种程度上,赢者通吃城市化是产业全球化的产物,赢者通吃城市化对全球城市排名洗牌的过程也是步产业全球化之后尘。 [11] 历史上,每个先进国家都有自己的汽车、钢铁、电子、化工产业,后来随着贸易壁垒的消失,它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竞争,很多公司被收购或者破产倒闭。产业全球化之前,各行各业的小企业各自占领本土市场,而产业全球化之后,大型跨国集团一统江山,霸占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幸存小企业则为了越来越小的剩余市场份额争得头破血流。
全球化也对世界城市排名进行了洗牌。随着资本主义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也就是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变得越来越精细,最有经济价值的地段和市场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几个城市。过去最顶尖的人才和最赚钱的行业分散在各个中小城市中,而现在这些人才和行业倾向于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城市。这些城市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最高峰”。“最高峰”们繁荣发展,“小山丘”们市场萧条,而面积更大的“平原”和“山谷”们则苦不堪言。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与菲尼克斯、达拉斯、大西洋城等“太阳地带”城市不同,像纽约、伦敦、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市或者像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这样的知识中心都没有经历过高水平的人口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并不是超级城市强大实力的来源,因为这些城市的优势在于质量而非数量。超级城市是富人和优势群体的根据地,很多人因为无力承担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只能迁往美国南部的“太阳地带”城市,进而拉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有人认为,超级城市和科技产业中心的高昂物价会导致一些核心行业的企业搬去成本更低廉的地方,由此促成所谓的“其他地区的崛起”。这确实会减少一些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那样,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些高科技企业会撤离超级城市或科技产业中心,即使有迹象,也是显示它们会更加集中在这些地区。
房价能明确反映超级城市的主导地位以及它们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因此,我的研究团队利用Zillow(提供免费房地产估价服务的网站)的数据追踪了全美11000多个邮编地区的房价。结果显示,160个邮编地区的房价中位数高于100万美元,其中有80%位于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大都市;28个邮编地区的房价中位数超过200万美元,其中有24个分别在旧金山湾区(11个)、洛杉矶(7个)和纽约(6个)。2016年,旧金山城区里约57.4%的房屋价值超过100万美元,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0%。 [12] 对比之下,全美56.2%的邮编地区房价中位数低于20万美元,更有约15%的邮编地区房价中位数低于10万美元。
图2.1展示了纽约苏荷区公寓和其他城市住宅的等值关系,直观说明了其他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巨大差距。用一套苏荷区公寓的价格(中位数约300万美元)能在拉斯维加斯买18套房屋,在纳什维尔买20套房屋,在亚特兰大买23套房屋,在底特律买29套房屋,在克利夫兰买30套房屋,在圣路易斯买34套房屋,在孟菲斯买38套房屋。如果只考虑个别邮编地区,差异更大。一套苏荷区公寓价值相当于托莱多某些地区的50套房产或者底特律某些地区的70套房产。在俄亥俄州马霍宁县杨斯顿的某个社区,100多套房产才相当于纽约一套苏荷区公寓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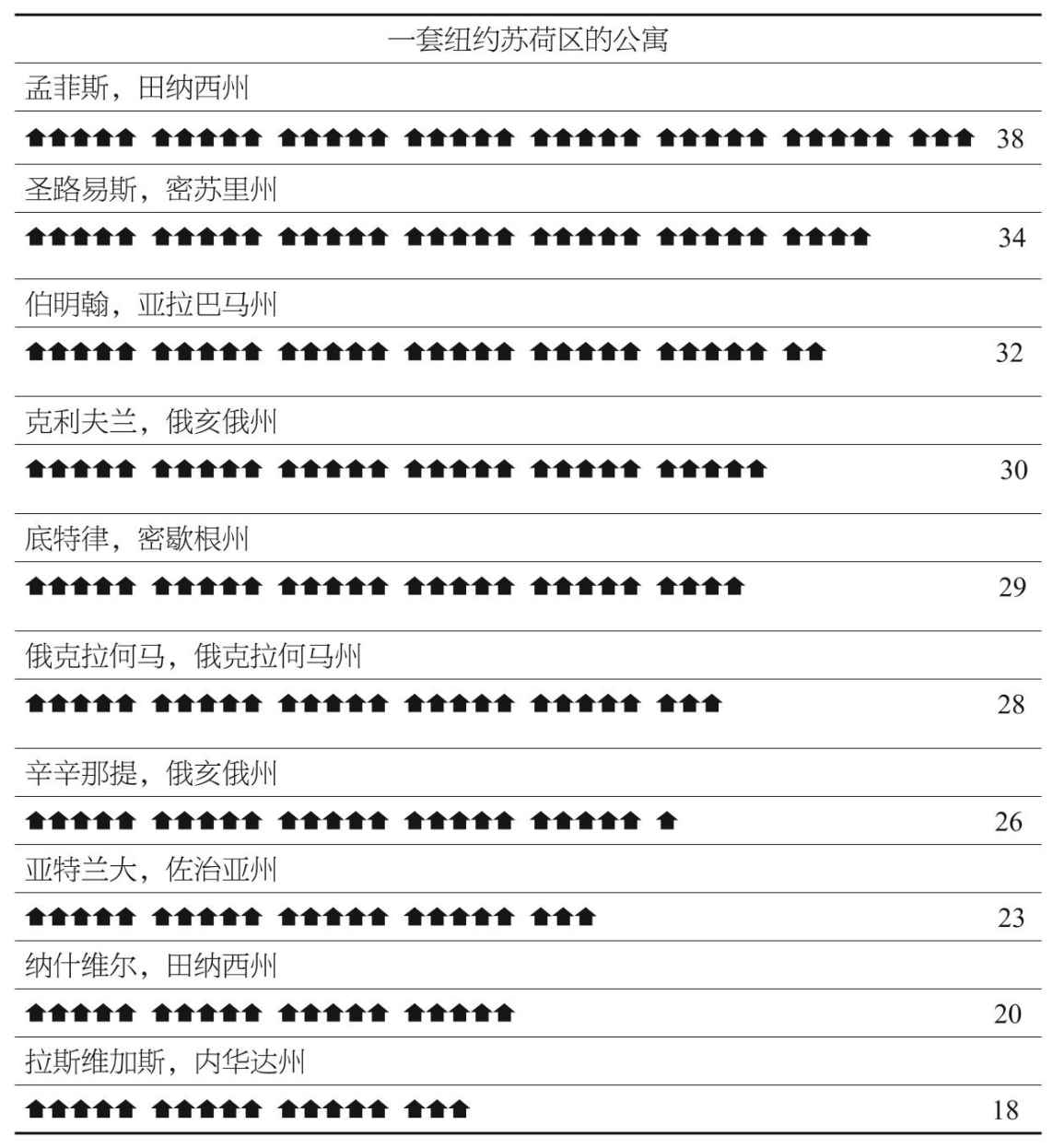
图2.1 一套纽约苏荷区的公寓可以在其他城市买多少套房屋?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Zillow2015年的数据。
但是,超级城市的光环只笼罩着城里少数几个区域。2015年底,曼哈顿的房屋均价已经超过200万美元,而纽约市房价中位数仅为60万美元,远低于市里某些地区的房价。苏荷区的房屋业主卖掉一套公寓就可以在纽约市北边的帕克彻斯特社区买30套住宅,那里的房屋均价仅为107067美元。超级城市自身也成了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受害者,逐渐分裂为少数高端社区和大量欠发达区域。
造成超级城市和高端社区房价高企,并导致它们与其他地区房价产生巨大差距的“元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引擎:聚合力。城市提供两种主要的聚合效应。一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企业和行业的聚合。早在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提出互相竞争的企业聚集于一处时所产生的效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深入研究过企业聚集是如何影响经济地理学并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为行业聚集提供了土壤,例如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业、洛杉矶的电影业、米兰和巴黎的时尚产业、圣何塞的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专业人才和野心家的聚合。简·雅各布斯最早提出多元化人才和技能的聚合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将自己对人才聚合效用的研究进行整合,形成了一套基于人力资本外部效用的经济理论。超级城市让世界各地的人才跨越了种族、国籍和性取向的差异,聚集在一起。在旧金山湾区,过去10年间成立的高科技创业公司中约有1/3到一半的企业至少有一名移民创始人。 [13]
但是,城市通过聚合力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导致了城市自身的根本矛盾。聚合效用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对有限城市空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一个地方聚集的人才和企业越多,土地就越贵,房价也就越高,最后必然导致部分居民和企业被挤出。城市经济学家威廉·阿朗索在1960年发表的名为“城市土地市场理论”(A Theory of the Urban Land Market)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简洁优雅的城市空间竞争模型。在他看来,土地价格遵循一条距市中心越远、地价越低的竞租曲线。 [14] 那时,大企业总部占据城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向外一层是对地段要求较高的工厂和库房,再向外一层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工薪阶层,他们住在工业区附近,生存环境拥挤、吵闹、脏乱。比较殷实的家庭为了避开这种环境,选择居住在更远的郊区。但现如今,富人占据了过去只有工商业的中心地带,令中心城区房地产价格飙升。高度开发且生产效率极高的土地供应十分有限,带来了城市土地关系的核心——对空间的激烈竞争。
再来看看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溢价。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美土地价值共计23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家经济产出的160%。 [15] 但仅6%的已开发土地价值就共计11.7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美土地价值的一半。全美已开发土地平均价格是未开发土地的16倍,每英亩 [02] 均价分别为106000美元和6500美元。人口数大于100万的大城市土地均价为64800美元/英亩,人口数少于100万的大城市土地均价为16600美元/英亩,而人口数在1万至49000人之间的小城市土地均价仅为6700美元/英亩。
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些城市的高端社区房价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些社区的房价往往是每平方英尺 [03] 1500美元、2000美元、3000美元或者更高,而美国普通房屋均价为每平方英尺150~200美元。事实上,美国所有超级城市的房地产价值总量已经赶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了。2015年,纽约市城区的房地产总值约为2.9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泛洛杉矶地区的房地产总值约为2.8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泛旧金山地区的房地产总值是1.4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者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所有住宅地产总价值约为35万亿美元(其中业主自有产权房产占28.4万亿,出租物业占5.8万亿),已经超过了中美两国经济产出之和。 [16]
超级城市的房价远超其他地区的现象历史已久。1950年,超级城市房价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到2000年这一比例变成了四倍,如今还在扩大。 [17] 从1995—2000年,旧金山的房价增幅为每年3.5%,而同期美国所有人口超过200万(截至2000年底)的大城市平均房价增速仅为每年1.7%。
但超级城市真正的房价飙升出现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因为资源过度聚集导致对稀缺土地的竞争越发激烈。从图2.2可以看出,从1950—1993年,纽约市的房价增速为每年不到0.5%,而在那之后的土地价格便急速上升,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经历了短暂暴跌,然后又重攀历史新高。如果一个投资者在1950年买了一块地并在1993年卖掉,那么在扣除通货膨胀损失后他的年收益率不到0.5%。但如果他在1993年买了一块地并持有至2014年,他就能以28倍于成本的价格把它卖掉,年收益率达到16.3%。
曼哈顿的土地升值幅度远高于其他形式的房地产。在1994—2014年的20年间,土地投资的年收益率约为15%(精确值为14.9%),三倍于独立产权公寓投资的年收益率(4.4%)。 [18] 这就是城市土地关系的症结:高端小区有限的土地资源阻碍了土木工程的伟大壮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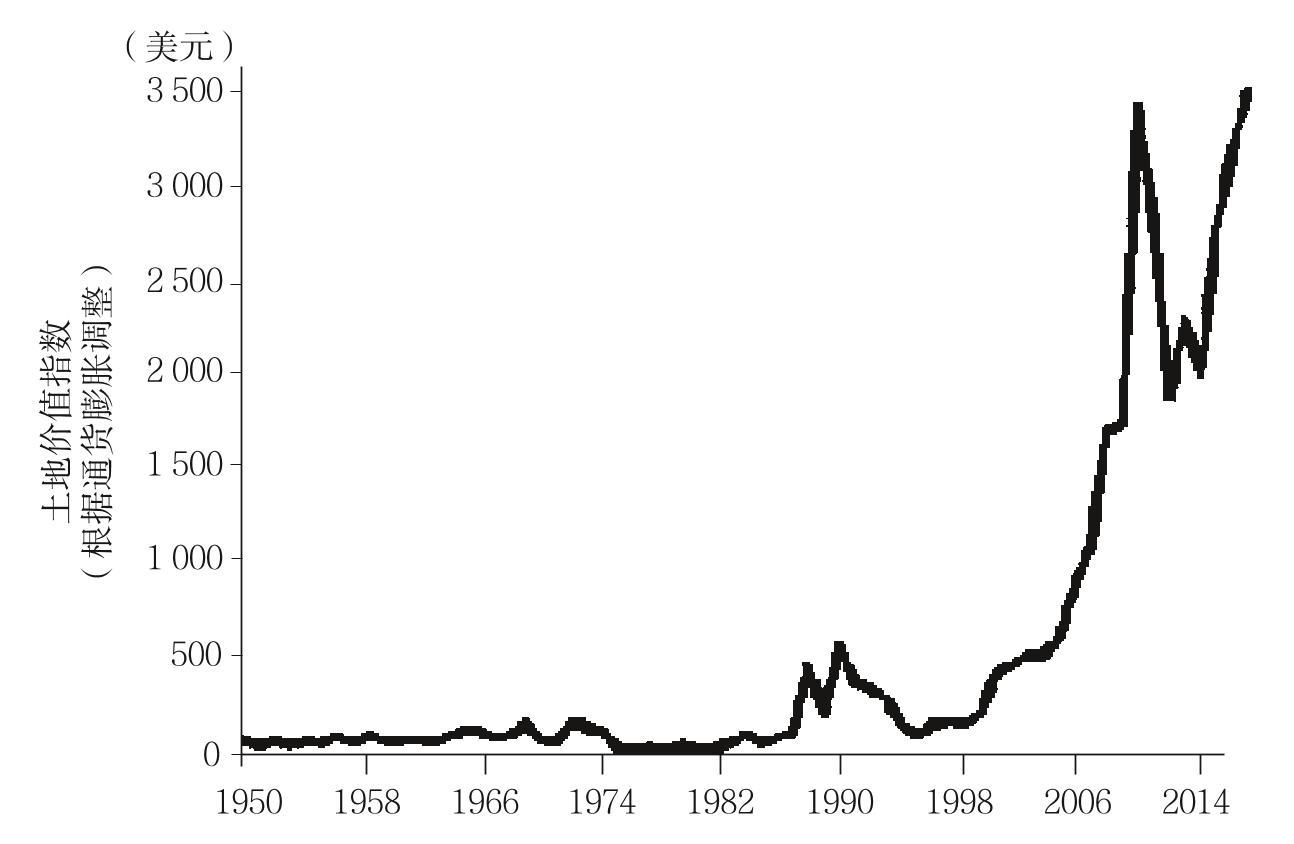
图2.2 纽约市的土地价值变化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杰森·巴尔、弗雷德·史密斯、萨亚利·库尔卡尼,“曼哈顿值多少钱?1950—2014年土地价值指数”,罗格斯大学2015-002工作论文,2015年3月,http://econpapers,repec.crg/paper/runwpaper/2015-002.htm。图形来自安娜·谢尔比纳和杰森·巴尔,“曼哈顿房地产:下一步是什么?”,真实清晰市场网,2016年2月8日,www.reald ear markets.com/artides/2016/02/08/manhattan_real_estate_whats_nect_101995.html。
注:土地价值指数反映的是1950年1月100美元经过通货膨胀后投资于一块标准土地的价值。
城市土地关系不仅是有限的供给与不断增加的需求的产物,它还是由城市土地所有者和房屋业主造成的,这些再城市化的最大赢家通过限制新房屋建设以维持自己持有房地产的高价值。越来越多城市经济学家指出,导致城市房价虚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邻避” [04] 主义。“邻避”最初是指居民阻止在自己的社区修建监狱、废物处理厂等“不好的”公共设施的行为。最近几年,“邻避”现象越来越频繁。自1970年以来,美国有关“土地使用”的诉讼案件大幅增加,而“土地使用”就是“邻避”的代名词。 [19]
我的一篇专栏文章惹恼了“邻避”的拥护者,因为我建议多伦多政府认真考虑允许噪声较小的新型小型喷气式飞机在比利·毕晓普机场起降的提案,而这个机场离多伦多市中心很近。提出此建议是因为我的一项研究表明,机场是最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发展引擎之一。目前,比利·毕晓普机场只有通往蒙特利尔、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的短途航线。大家讨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延长跑道,允许小型喷气式飞机起降,以此增加飞往温哥华、洛杉矶、迈阿密甚至是伦敦和巴黎的长途航线。我认为政府既应该考虑可能给海滨地区带来的噪声和交通成本,也应该考虑一个充满活力的市中心机场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我在专栏中写道,既然现在多伦多的海滨地区已经十分拥挤嘈杂,难道不应当更充分考虑这些小型喷气式飞机能给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吗? [20] 我们永远不能提前预知结果。批评者认为我只顾自己的便利而不顾城市的安宁,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最后,由于市民和社会活动分子持续施压,贾斯廷·特鲁多政府为兑现竞选承诺,否决了这项提案。
虽然社区和环境保护确有必要,但“邻避”拥护者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仅是把所谓的“不好的”公共设施挡在城市和社区之外了。不论初衷如何,他们本能地阻止任何发展的行为在保住了自己房价的同时,也抑制了驱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引擎——聚合力。
多数情况下,“邻避”反映了经济学中的寻租行为。“寻租”本质上就是付出极小代价获得的超额回报。还有什么比坐在自己的房子里看着它不断升值更简单的事呢?尤其是当升值全依赖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时候。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就对没有生产力的寻租行为表示担忧。在那时,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而非资本。在18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了“土地价值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先驱。坎蒂隆把经济参与者分成两类 [21] ,一类是用劳动换工资,再用工资换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者,另一类是优势阶层,但与马克思定义的资本家优势阶层不同,坎蒂隆定义的优势阶层由地主构成,他们通过转让房屋使用权获得的租金回报积累财富。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租金理论”,描述地主仅因对土地的所有权而获得暴利,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使用土地固有的不可毁灭的力量而付给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作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抨击了地主的自私和懒惰。
如今,相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可使用土地的稀缺性更能使寻租者提高收益。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经济学人》编辑瑞安·埃文特所说的“寄生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自有房产的相对富裕人群获得远超其人口比例的经济产出和财富。一位经济学家曾尖锐地指出,“吸光所有经济财富的是地主,而非企业家”。 [22]
这种行为不仅自私,还十分有害。“邻避”行为通过限制城市的企业聚集和人口密度,抑制了促进城市发展的创新活动,因此我愿意亲切地称他们为“新城市卢德分子”。以前的卢德分子以他们的半神话先驱内德·卢德命名,他们挥动铁锤,砸碎了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抢走他们饭碗的织布机。 [23] 然而讽刺的是,卢德分子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因工厂而大幅提高。不过以前的卢德分子都是穷人,新的城市卢德分子则不再是受剥削的工人阶层,而是“赢者通吃城市化”的最大赢家。
新城市卢德分子的主张影响了土地分区法和其他关于土地使用的法规,在很多城市,这些错综复杂的庞大法律体系限制了房屋供应。虽然最初很多法规的目的只是保证在有毒副作用的工业生产与居民区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但林林总总的繁杂法规加起来,就对经济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2015年,两名前沿城市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表明,1964—2009年,限制住宅开发的政策导致美国损失了1.4万亿~2万亿美元的潜在经济收益。另外,虽然在此期间纽约贡献了全国经济总产出增幅的12%,但纽约超过一半的产出增长都被刻意抬高的房价吞噬了。他们估算,如果没有这些房屋和土地使用法规限制住宅开发,让每一个想在城市工作的人都能承担得起住房成本,旧金山就业岗位将增加5倍,纽约的就业岗位将增加8倍,全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将增加8775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3.5%,即近2万亿美元。这些估算数据警示人们,对土地的低效利用令美国经济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由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2016年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限制土地使用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危害。 [24]
更让人担忧的是,新城市卢德主义不仅限制了住房开发,还人为限制了未来城市的整体发展和扩张。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建造新学校、下水道、电网、交通和地铁线路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遣散附近居民的难度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这么少。在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新城市卢德分子不懈地阻挠着城市扩张,然而,城市扩张越少,聚合力就越弱,聚合力越弱,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就越低,结果就导致经济产出更少,税基更小,这又进一步约束了城市投资发展和扩大再分配的能力。
毫无疑问,新城市卢德主义对新城市危机的形成负有极大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应当采取一定措施制约“邻避”行为,并精简现有的土地使用规定。但这并不代表应当废除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法规。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市场化城市分子”共同呼吁,应当废除现有土地使用法规,以此降低城市居住成本、缩小贫富差距及提高生产力。但他们的理念太过理想化了,根本不可行。一方面,高端小区土地价格高昂,私人市场很难甚至不可能在这些地区提供经济住房。高昂的土地价格和高昂的高层建筑成本决定这里只会出现更多的高档公寓,而超级城市紧缺的经济房屋则极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如果人口密度超过了这个转折点,社区就会失去活力。世界上最富创新力的不是亚洲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而是旧金山、纽约和伦敦那些适合步行的综合性社区。现代城市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废除法规,而是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并配套改革税收系统,扩大交通投资,逐步用租赁房屋代替独栋住宅,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城市化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密集人口、聚合力和多元化人才的碰撞。我在第十章会就这一点展开阐述。
事实上,相对于土地使用管制,城市土地关系面临一个更强硬的限制因素——地理位置。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本身就有高山、河流等硬性地理边界,这些因素与约束人口密度的法规一起对城市开发产生限制作用。我在图2.3中对1980—2010年城市的房价增长和住宅开发面积数据进行排列,说明了城市向外扩张和房价增长的反向变动关系,即城市向外扩张并创造新住房供给的能力越强,房价增长幅度就越小。图左上角的城市(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西雅图和华盛顿)住宅开发面积较小,房价增速很高;图右下角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亚特兰大、奥斯汀科技中心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市)的住宅开发面积则较大,房价增速较低。 [25]
地理位置也能从其他方面推高房价。像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老城市由于已被郊区包围,无法向外扩张,而那些年轻的“太阳地带”城市则可以自由征用城市周边土地。事实上,只有到达向外扩张的地理极限的城市才会在建设成熟的市区出现大幅人口增长,比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湾区、洛杉矶和迈阿密。从1960—2014年,12万人口从不断扩张的休斯敦市区的成熟社区流失,而实施土地使用限制法规的旧金山的成熟市区则出现了7万新增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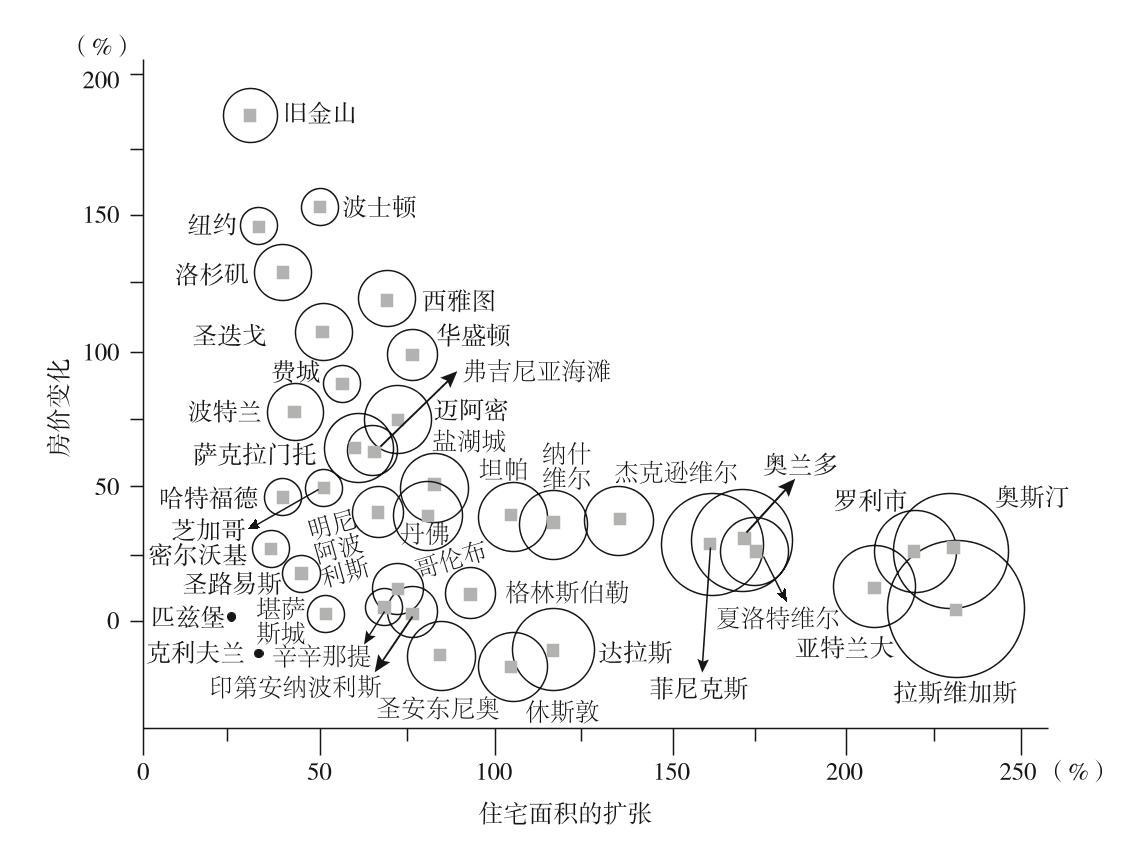
图2.3 部分美国城市地理位置与房屋价格的关系
资料来源:“美国城市的扩张放缓了吗?”,2016年4月18日,www.buildzocm.com/blog/cities-expension-slowing。
注:圆圈大小与人口增长成正比。
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艾伯特·赛斯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地理位置对房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土地使用法规。虽然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城市也有限制性土地使用法规,但地理位置才是房价暴涨的关键因素。 [26]
人们普遍认为工薪阶层在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内经济状况更好,尽管土地和住宅价格高昂,但工资报酬水平更高。因此,高新技术和知识产业聚集还为超级城市带来了关联行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由这种乘数效应引发的额外效用应运而生。 [27]
这一观点有数据支撑,表2.2分别列出了扣除住房支出后工薪阶层剩余工资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 [28] 。最高的五个城市都是技术中心和超级城市,硅谷中心圣何塞的工薪阶层平均每年剩余工资为48566美元,旧金山为45200美元,华盛顿为43308美元,波士顿和纽约分别为42858美元和42120美元,它们都远超奥兰多(25774美元)和拉斯维加斯(26194美元)。事实上,如果从整体收入水平来考量,不论是工薪阶层整体,还是其中的三个主要阶层(即高薪创意阶层、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都存在在大城市中收入较高,并且收入水平与城市人口规模呈正相关的现象。 [29]
表2.2 扣除住房支出后工薪阶层剩余工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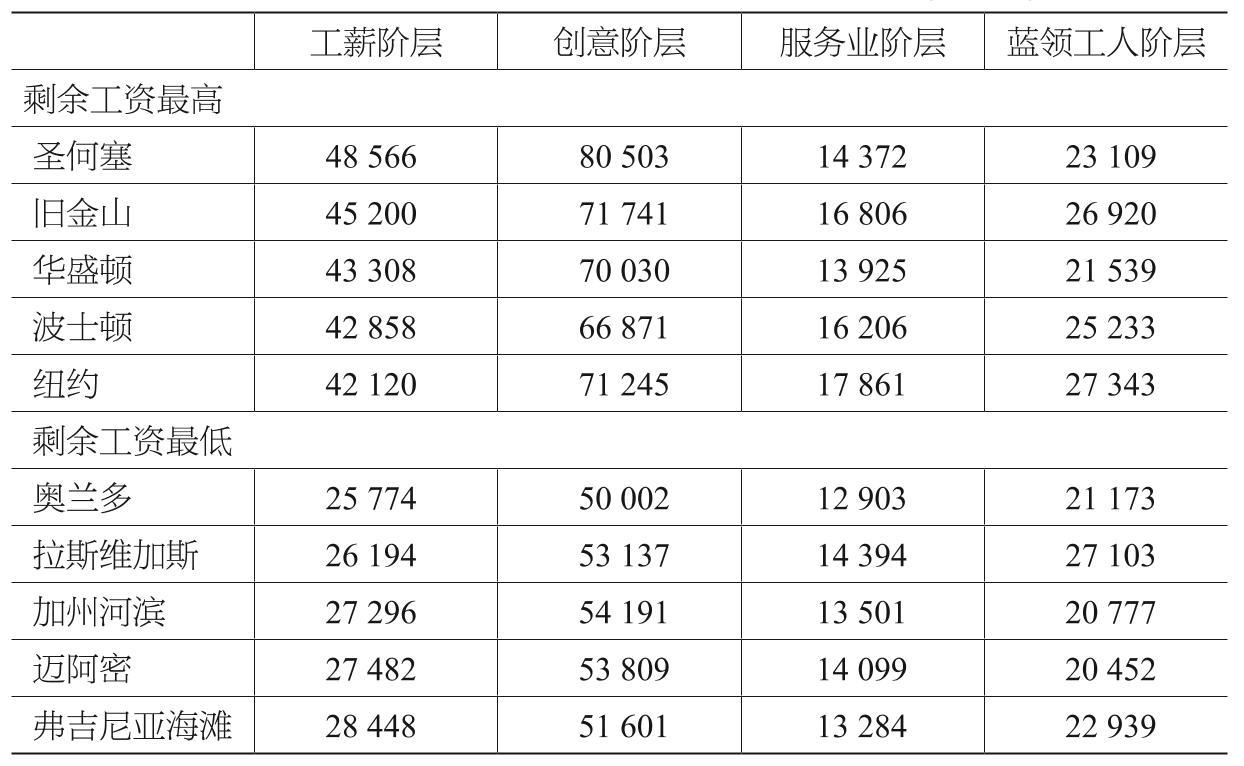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但是超级城市较高的剩余工资水平则主要归功于优势创意阶层的高收入。如果分别看三个阶层各自的情况,结果大相径庭。高收入的创意阶层完全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住房费用,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的经济状况则不容乐观。在圣何塞,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平均剩余工资为80503美元,而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的平均剩余工资分别为23109美元和14372美元;旧金山的数据分别为71741美元、26920美元和16806美元;纽约则为71245美元、27343美元和17861美元。
这种差别在发达城市中可能更为明显,但在其他350多个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工资与住房支出呈正相关性,但是对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来说,剩余工资则与住房支出呈负相关性。 [30] 由此得到的结论十分可怕:虽然超级城市极具创新活力和经济生产力,但优势阶层获得了最大的经济收益,而弱势的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则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收入增长赶不上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房价是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关键因素。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代际不平等的根源可以用著名公式“r>g”来表达,即资本回报率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资本的超高回报率更多来自不动产增值,而非股票或债券等资产的收益。马修·荣格侬利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现在,房地产增值占资本收入的比值已经翻了3倍,远超其他类型的资本回报。荣格侬利写道:“因为房产的所有权十分广泛,所以它不符合传统的劳动力与资本理论,它的增长也不能简单地用其他收入分化理论解释,如劳动者议价能力和科技地位的提升等。”换言之,这类收益完全是地段的租金。简单来说,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土地和房屋所有者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大赢家,他们彰显身份的顶层阁楼、豪华别墅和其他不动产就是皮凯蒂“r>g”公式的直观体现。 [31]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直面新城市危机的核心要素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聚合力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源头,人才与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少的几个城市聚集,不仅将世界城市划分为赢家和输家两个阵营,还让赢家城市越来越贵,变成顶尖优势群体的专属地盘。这个残酷循环只是单单有利于经济优渥的土地和房屋所有者,而对于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都不是好消息。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土地关系带来的冲突和矛盾,讨论它如何让三个群体——超级富豪、科技人员和商人、艺术家和其他文艺创作者为了空间相互竞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新城市危机中最明显的断层线是如何产生的。
[1] Geoff Manaugh and Kelsey Campbell-Dollaghan, “Sneak Peek of SimCity:Cities of Tomorrow,” Gizmodo, October 11, 2013, http://gizmodo.com/sneakpeek-of-simcity-cities-of-the-future-1443653857.
[2] 据我所知,超级城市一词最早来自2013年经济学家Joseph Gyourko、Christopher Mayer和Todd Sinai的研究报告,指房价上涨速度长期位于前列的美国城市。参见 “Superstar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 5, no. 4 (2013): 167–199。
[3] Robert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Penguin,1996); Sherwin Rose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no. 5 (1981): 845–858.
[4] 该比值到1978年上升至30倍,到1995年上升至123倍,到2000年(也就是弗兰克和库克的理论成型前后)到达383倍,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一直徘徊在在300倍左右。参见 Lawrence Mishel and Jessica Schieder, “Stock Market Headwinds Meant Meant Less Generous Year for Some CEO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12, 2016, www.epi.org/files/pdf/109799.pdf; Ric Marshall and Linda-Eling Lee, Are CEOs Paid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quity Incentives, MSCI Research Insight, July 2016, www.msci.com/documents/10199/91a7f92bd4ba-4d29-ae5f-8022f9bb944d; Theo Francis, “Best-Paid CEOs Run Some of Worst-Performing Compani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16,www.wsj.com/articles/best-paid-ceos-run-some-of-worst-performingcompanies-1469419262. 不难想像,这项研究呼吁大幅削减股权薪酬。
[5] 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德里克·汤普森称之为“富人更富原则“。参见 Derek Thompson, “The Richest Cities for Young People: 1980 vs. Today,”The Atlantic, February 15, 2015,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2/for-great-american-cities-the-rich-dont-always-get-richer/385513。
[6] 超级城市指数使用了五个指标,第一个指标衡量经济实力,基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都市观察报告的经济产出和人均经济产出数据,参见Joseph Parilla, Jesus Leal Trujillo, and Alan Berube, Global Metro Monitor 2014:An Uncertain Recover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bmpp_GMM_final.pdf?la=en. 第二个指标衡量金融实力,基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该指数评估城市的银行、金融和投资业发展状况,参见Mark Yeandle, Nick Danev, and Michael Mainelli,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Z/Yen Group, 2014, www.zyen.com/research/gfci.html. 第三和第四个指标衡量全球竞争力,分别是《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veness)和A. T. Kearney的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这两个指标追踪全球城市的商业活动、人才和竞争力情况,参见Citigroup, Hot Spots 2025:Benchmarking th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3, www.citigroup.com/citi/citiforcities/pdfs/hotspots2025.pdf; Mike Hales, Erik R. Peterson, Andres Mendoza, and Johan Gott, Global Cities,Present and Future: 2014 Global Cities Index and Emerging Cities Outlook,AT Kearney, 2014, www.atkearney.com/research-studies/global-cities-index/full-report. 第五个指标衡量生活质量,基于联合国城市繁荣指数(UN City Prosperity Index),该指数从生产力、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公平与社会包容度以及环境可持续性这五个方面评估城市的繁荣程度,参见联合国人居署,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3),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745habitat.pdf。
[7] Richard Florida, “The World Is Spiky,”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2005), 48–51,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mages/issues/200510/world-is-spiky.pdf.
[8] John Schoales, “Alpha Clusters: Creative Innovation in Local Economies,”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 no. 2 (2006): 162–177.
[01] “纽约的一分钟”,形容顷刻之间。——译者注
[9] 例如, Luís M. A. Bettencourt, José Lobo, Deborah Strumsky, and Geoffrey B.West, “Urban Scaling and Its Deviations: Revealing the Structure of Wealth,Innovation, and Crime Across Cities,” PLOS ONE (November 10, 2010)。
[10]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Steven Pedigo, and Rosemary Scanlon,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July 2015,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default.html#page/1.
[11] Richard Florida, “Why Some Cities Lose When Others Win,” CityLab,March 30,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why-some-cities-losewhen-others-win/1611; Aaron M. Renn, “The Great Reordering of the Urban Hierarchy,” New Geography, March 26, 2012, www.newgeography.com/content/002745-the-great-reordering-urban-hierarchy.
[12] 数据来自Zillow’s Research Data网站, www.zillow.com/research/data. 需要注意的是,Zillow的数据排除了以下的数据保密州: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即便如此,Zillow还是为我们观察超级城市和超级社区与其他地方的房价差距提供了有益参考。
[13] 关于聚合力的问题,参考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Macmillan, 1890);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 Paul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no. 3 (June 1991): 483–499; Robert E.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 1 (1988): 3–42. On diversity and immigration, see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ivek Wadhwa, AnnaLee Saxenian, and F. Daniel Siciliano, 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Then and Now (Kansas City, MO: Kauffman Foundation, 2012), www.kauffman.org/~/media/kauffman_org/research%20reports%20and%20covers/2012/10/then_and_now_americas_new_immigrant_entrepreneurs.pdf。
[14] William Alonso, “A Theory of the Urban Land Market,” Regional Science 6,no. 1 (1960): 149–157; William Alonso, Location and Land Us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5] Willie Larson, New Estimates of Value of 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5, www.bea.gov/papers/pdf/new-estimates-ofvalue-of-land-of-the-united-states-larson.pdf; Richard Florida, “The Real Role of Land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ityLab, April 10,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4/the-real-role-of-land-values-in-the-unitedstates/389862.
[02] 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编者注
[03] 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编者注
[16] 数据来自Joe Cortright, “The Market Cap of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January 1 2016, http://cityobservatory.org/the-market-cap-of-cities. Cortright 结合了Zillow网站对自有房产的估值28.4万亿美元和他自己对租赁房产的估值5.8万亿。他在邮件中解释,他利用Zillow网站上年租金原始数据估测租赁房产价值。例如,为了得到美国租赁房产总价值,他用Zillow网站提供的年租金总额5350亿美元的和65%的净营业收入比计算得到租赁市场净收入3500亿美元,然后除以6%的资本收益率的得到5.8万亿的总值。自有房产和租赁房产的原始数据都来自Svenja Gudell,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Buy Every Home in America?” Zillow Blog, December 30,2015, www.zillow.com/research/total-housing-value-2015-11535。
[17] Gyourko, Mayer, and Sinai, “Superstar Cities.”
[18] 数据来自Anna Scherbina and Jason Barr, “Manhattan Real Estate: What’s Next,” Real Clear Markets, February 8, 2016, www.realclearmarkets.com/articles/2016/02/08/manhattan_real_estate_whats_next_101995.html。
[04] 邻避(NIMBY),是“Not In My Backyard”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别在我家后院”。——译者注
[19] “邻避“(NIMBY )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也有人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参见 Michael Dear,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8, no. 3 (1992): 288–300. There is a rapidly expanding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NIMBYism and land use restrictions on housing cos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e, Edward Glaese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New York: Penguin, 2011); Ryan Avent, The Gated City (Seattle: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2014); Ryan Avent, “One Path to Better Jobs: More Density in Citi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11, www.nytimes.com/2011/09/04/opinion/sunday/one-path-to-better-jobs-more-density-in-cities.html; Matthew Yglesias, 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2); Matthew Yglesias, “NIMBYs Are Killing the National Economy,”Vox, April 25, 2014, www.vox.com/2014/4/25/5650816/NIMBYs-arekilling-the-national-economy. On the increase in court cases about land use issues, see Peter Ganong and Daniel Shoag,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2015,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81216。
[20] Richard Florida, “Bring on the Jets at Island Airport,” Toronto Star,December 17, 2013, www.thestar.com/opinion/commentary/2013/12/17/bring_on_the_jets_at_the_island_airport.html;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homas Holgersson, “Up in the Air: The Role of Airport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54, no. 1(2015): 197–214; Jordan Press, “Trudeau Government Says No to Expansion of Toronto Island Airport,” Toronto Star, November 21, 2015, 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15/11/27/trudeau-government-says-no-to-expansion-oftoronto-island-airport.html.
[21] Hans Brems, “Cantillon Versus Marx: The Land Theory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0, no. 4 (1978): 669–678; Anthony Brewer, “Cantillon and the Land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no. 1 (1988): 1–14; David Ricardo, “On Rent,” in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21), chap. 2, available at www.econlib.org/library/Ricardo/ricP.html;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ntam Classics Reprint [New York: Bantam, 2003 (1776)].
[22] Ryan Avent, “The Parasitic City,” The Economist, June 3, 2013, 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3/06/london-house-prices; Noah Smith, “Piketty’s Three Big Mistakes,” Bloomberg View, March 27, 2015,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03-27/piketty-s-three-big-mistakesin-inequality-analysis. Emphasis is from the original.
[23] 关于旧卢德分子的讨论,参见Kirkpatrick Sale,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essons for the Computer (Boston: Addison-Wesley, 1995)。
[24] Chang-Tai Hsieh and Enrico Moretti, “Why Do Cities Matter? Local Growth and Aggregate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15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5. 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Jason Furman和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董事Peter Orszag提到,“最好把城市区域规划法规理解为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限制,这些法规通过限制建筑高度、规定最小单位面积、给多户住宅设置复杂的审批流程或直接禁止修建多户住宅等方式有效限制某一区域内的建筑数量。”参见他们的著作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和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活动“一个公平的社会”上的演讲, October 16, 2015, 7–8, 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page/files/20151016_firm_level_perspective_on_role_of_rents_in_inequality.pdf. 也参见2016年总统经济报告的“Inclusive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2016), chap. 1, p. 44.除此之外,这类法规也加深了贫富群体的地理隔离和孤立,参见Michael C. Lens and Paavo Monkkonen,“Do Strict Land Use Regulations Make Metropolitan Areas More Segregated by Inc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2, no. 1 (2016):6–121. 这种土地使用法规太过严苛,所以也被称作“新排他性区域规划”。参见John Mangin, “The New Exclusionary Zoning,” Stanford Law and Policy Review 29, no. 1 (January 2014): 91–120; William Fischel,Zoning Rules! The Economics of Land Use Regulat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5。
[25] 数据和图表来自房地产网站BuildZoom首席经济学家伊希斯·罗门的研究,参见 Issi Romem, “Has 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Cities Slowed Down?”BuildZoom, May 15, 2016, www.buildzoom.com/blog/cities-expansion-slowing.该部分讨论也参考了Richard Florida, “Blame Geography for High Housing Prices?” CityLab, April 18, 2016, 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4/blamegeography-for-high-housing-prices/478680. 奥斯汀的数据有一定的欺骗性:该地区虽然房价增速温和,但存在严重的住房负担问题:它的房价可能低于旧金山,波士顿或华盛顿,但收入中位数也更低,约一半租房者面临沉重的居住成本负担。
[26] Albert Saiz, “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no. 3 (2010): 1253–1296; Yonah Freemark,“Reorienting Our Discussion of Urban Growth,” The Transport Politic, July 6,2016, www.thetransportpolitic.com/2016/07/06/reorienting-our-discussionof-city-growth. Freemark记录了美国前一百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对比了这些城市的总人口、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英里4000人的地区)的变化、以及市中心区域(以市政厅为中心方圆1.5到3英里的区域)的人口变化。
[27] 参见Enrico Moretti,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2)。
[28] Richard Florida, “Cost of Living Is Really All About Housing,” CityLab,July 21,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07/cost-of-living-is-reallyall-about-housing/373128; Richard Florida, “The U.S. Cities with the Most Leftover to Spend… After Paying for Housing,” CityLab, December 23,2011, www.citylab.com/housing/2011/12/us-cities-with-most-spend-afterpaying-housing/778.
[29] 平均工资与城市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0.58),并且这一关系适用于所有三个劳动力阶层:知识、专业与创意阶层(0.69)、服务业阶层(0.46)和蓝领工人阶层(0.28)。
[30] 住房成本与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剩余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58),与服务业阶层和蓝领工人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剩余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36和-0.20)。
[31]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tthew Rognlie,“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15, www.brookings.edu/~/media/projects/bpea/spring-2015/2015a_rognlie.pdf. 虽然有人批评罗格利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皮凯蒂的观点,但我认为它明确了住房在不平等加剧问题中扮演的角色。Felix Salmon referred to the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r>g” in his “Lessons from a $110 Million Penthouse,”Medium, June 8, 2014, https://medium.com/@felixsalmon/lessons-from-a-110million-penthouse-ca23db711df2。
2013年,著名新浪潮乐队“传声头像”的主唱大卫·拜恩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纽约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开始扼杀创意人才,我就会离开纽约。” [1] 他认为纽约高速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文化灾难,“多数曼哈顿社区和部分布鲁克林社区基本已是富人区,中产阶级已经很难负担得起纽约的生活成本,就更别提那些年轻艺术家、音乐人、演员、舞蹈演员、作家、记者和小生意人了,城市的活力源泉在慢慢消失”。
拜恩不是唯一提出警告的。著名朋克摇滚歌手、诗人、传记作家以及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帕蒂·史密斯在被问及年轻人还能否在纽约做出一番事业时回答:“纽约已经不属于年轻人和想白手起家的奋斗者了,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比如底特律和波基普西。总之,我的建议是换个地方。” [2]
2014年,电子音乐人莫比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花140美元就能在14街与几个形形色色的音乐人和艺术家一起合租公寓。那时纽约艾滋病蔓延、经济萧条、谋杀率居高不下,大家都避之不及。但即便如此,曼哈顿仍是世界文化之都,其混乱而危险的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文化繁荣。当然,后来一切都变了,纽约成了金钱之都,人们认为房租占薪水的30%很正常,对一些人来说,曼哈顿现在的房租甚至是他们薪水的300%。” [3]
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和艺术家都亲身体会到了城市转型带来的影响。 [4] 事实上不只他们,很多学者和政客也开始担忧超级城市可能会抑制创新。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高级顾问、促成伦敦科技繁荣的关键人物罗恩·席尔瓦曾说:“很多人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矶,我们应警惕这种人口流失现象在伦敦上演。失去艺术家的后果很严重,城市会失去领先地位。” [5]
富有创造力的城市生态系统需要立足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如果没有城市融合带来的骚动,城市会了无生趣。在如今的苏荷区,奢侈品商店似乎比演出场所和艺术工作室还多,富人纷纷迁入城市核心地带。但即便是房价飙升导致年轻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越来越难在苏荷等社区立足,一些主要的创意社区都在转型,城市也没有失去创新活力,变得死气沉沉,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城市的创新能力有所下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通过把创新和科技行业融入自己的经济中来巩固自己的创新优势。毕竟,城市规模很大,创造力可以在社区之间转移。不排除城市变革在将来危及超级城市创新能力的可能性,但目前还言之过早。
拜恩、莫比和史密斯的担忧其实反映了城市空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艺术家、音乐人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愿意把废弃的城市空间改造成工作室,但现在他们却遭到了金融人士、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的排挤。以纽约的西切尔西区为例,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肮脏的工业区,后来廉价的阁楼和公寓吸引来一批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也包括很多同性恋,于是这里开始出现酒吧、画廊和餐馆。慢慢地,社区越来越安全而富有魅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开始迁入,带来了高端的商场、餐馆和酒店,艺术家的阁楼和工作室也逐渐被创业公司和科技企业取代。高线公园的建成是社区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拐点,这里开始变成高端公寓聚集地,以迎合更富裕人群的需求。
创意工作者认为他们在城市土地战争中的对手是更富裕的阶层。然而尽管绝大部分创意工作者算不上真正的富人(拜恩、史密斯和莫比除外),但以普通美国人的标准看,他们也属于相对优势人群。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在纽约,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52750美元,低于科技人员(659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8700美元),但已是服务业从业者(17860美元)的约3倍;在洛杉矶,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和纽约差不多,为53760美元,低于科技人员(6435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7587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5350美元)的3.5倍有余;在旧金山,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47200美元,仍然低于科技专家(700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490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6800美元)的近3倍。 [6]
这并不代表超级城市中所有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经济状况都不错,很多人状况并不容乐观,甚至不得不离开原来生活的社区。但经验表明他们的整体经济状况更接近优越的城市精英群体,而不是相对劣势的服务业阶层。
随着超级富豪涌入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新一轮城市空间竞争开始了。在这一章,我将先对竞争的根源和本质进行讨论,然后探讨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和科技从业者从传统郊区涌入城市中心的现象,最后通过数据分析拜恩、史密斯和莫比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房价上涨和富豪涌入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相关数据导向一个明确结论:迄今为止,所谓的城市创造力消亡只不过是谣言。新城市危机的症结不是新城市精英内部的派系冲突,而是弱势群体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最近几年,我每次去伦敦都能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在途经海德公园往返机场的路上,司机一定会指着文华东方酒店旁的现代玻璃大楼说:“看见那栋楼了吗?那儿有5000多万美元的公寓,但根本没人住,晚上永远黑漆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2014年,伦敦的高端社区里至少有740套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公寓无人居住。
纽约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曼哈顿,闲置公寓数量从2000年的19000套增加到2001年的34000套,增长率接近70%;在上东区,一片占地三个街区的区域里有57%的公寓每年的闲置时间长达10个月。 [7]
越来越多的评论员认为全球超级富豪正逐步占领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城市。2013年和2014年,外国购房者(包括伦敦市居民和非居民)买下了伦敦市中心地段近一半售价高于100万英镑的住宅。伦敦高端社区里上演的激烈空间竞争意味着过去的“绅士化”开始转变为“富豪化”或“寡头政治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被富有的外国购房者挤出高端社区的不仅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还包括一些传统精英阶层与富贵世家。虽然在如今城市贫富差距之大史无前例、工人阶级住不起房子、穷人只能蜗居在破烂社区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那些把房产以天价卖给购房者并大赚一笔的外国富人,但这也足以反映,超级城市部分昂贵地段已经成了镀金的全球富豪聚集区,而且还被大量闲置。 [8] 除了富豪之外,大型公司、房地产投资信托、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在超级城市大手笔购房置业。全球城市专家萨斯基雅·萨森估计,到2015年,企业对城市房地产的投资总和已超过10000亿美元。《纽约时报》通过对高端建筑群时代华纳中心的详尽调查,披露了超级富豪普遍用空壳公司隐藏身份的现象。新建的卡耐基57号大楼的售价在纽约市名列前茅,超过3/4的业主都用匿名公司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9]
富豪在超级城市置业并不是传统的住宅购置行为,这些房屋没有人居住,只是一种安全的财富保值手段。托斯丹·范伯伦认为,在20世纪初,购买高端房产就是用来衡量和展示财富实力的炫耀性消费。而现在高端房产变得实用多了,属于用来对财富保值增值的新经济资产类别。 [10]
大量证据表明,纽约和伦敦确实聚集了大量富人,其中伦敦千万富豪数量最多,而纽约的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5370亿美元(见图3.1);在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上紧随纽约之后的是旧金山湾区(包括硅谷),它拥有的71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3650亿美元;莫斯科排名第三,68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29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的亿万富豪多为寡头集团掌控者,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下跌和卢布贬值导致他们的资产大幅缩水,我们也能从本书第二章看到,莫斯科在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中排名靠后);香港排名第四,有64位亿万富豪;洛杉矶排名第五,有51位亿万富豪;伦敦排名第六,有50位亿万富豪。伦敦比纽约更依赖海外资产:伦敦的50位亿万富豪中有26位是外国人,占比超过50%;而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中只有10位是外国人,占比低于10%。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前十的其他城市依次为北京(46位)、孟买(33位)、迈阿密(31位)和伊斯坦布尔(30位)。排行榜再往下看,七个城市拥有20~30位亿万富豪(首尔、巴黎、圣保罗、深圳、台北、达拉斯和新加坡),三十个城市拥有10~20位亿万富豪(华盛顿、波士顿、亚特兰大、菲尼克斯、西雅图、多伦多和墨西哥城等)。总的来说,城市人口越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越强,金融和科技产业规模越大,亿万富豪数量越多,并且富豪的总资产净值越高。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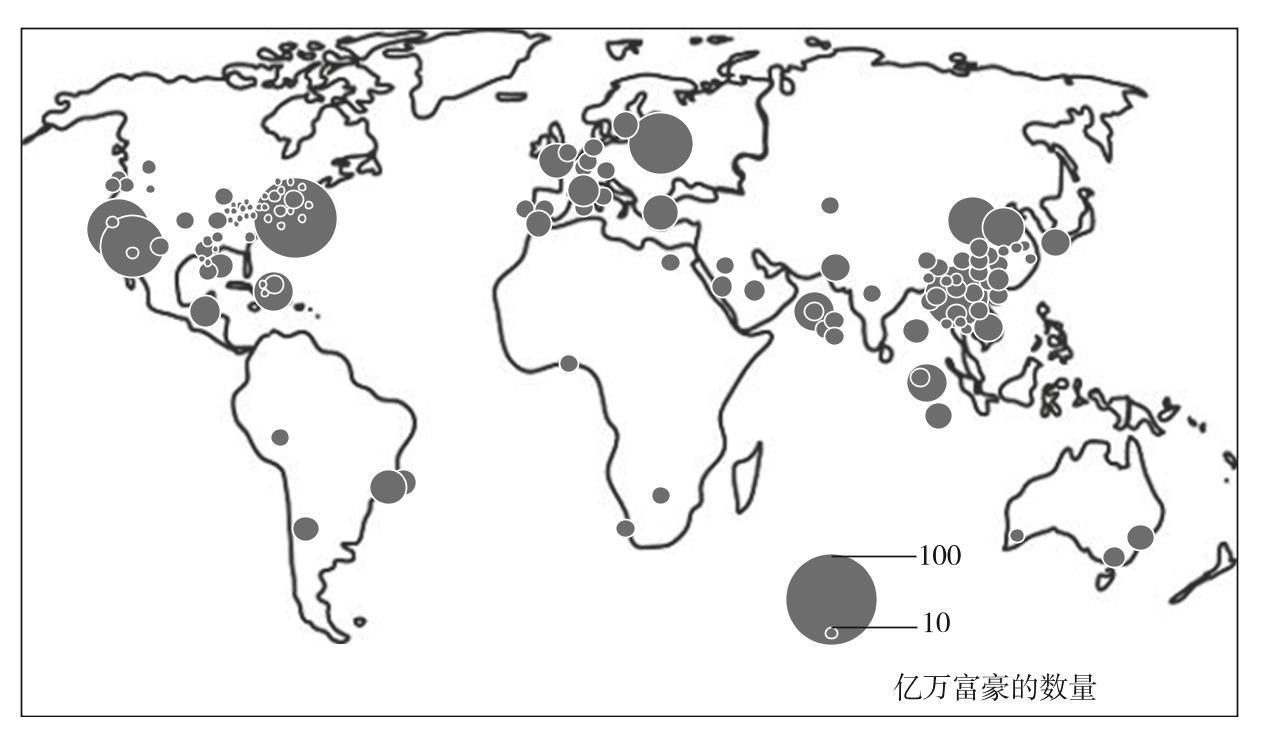
图3.1 亿万富豪都住在哪里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福布斯》,2015年。
图3.2展示了更广义的富人群体——即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所谓“超高净值人群”的全球分布情况。占全球人口0.002%的173000位千万富豪共拥有约20万亿美元的财富。 [12] 在千万富豪城市排行榜中,伦敦以拥有4364位千万富豪占据榜首,东京、新加坡、纽约和香港位列其后。
但这是个问题吗?超级富豪真的会对伟大城市造成负面影响吗?尽管少有人住的奢华住宅确实令某些社区缺乏活力,但超级富豪的数量远不足以抑制整座城市或整个核心城区的发展。纽约市有800多万居民和约300万套住宅,而116位亿万富豪加上约3000位千万富豪甚至填不满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一半的座位。另外,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全球购房热潮从2016年就开始降温了。因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石油国家)自身经济状况堪忧,还面临货币贬值的问题,同时美国开始管制海外投资者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包括一些实为洗钱的交易。总之,伟大城市的入侵者与其说是超级富豪,不如说是人口庞大的优势阶层,比如卖掉郊区住宅而到超级城市购房的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和高薪的科技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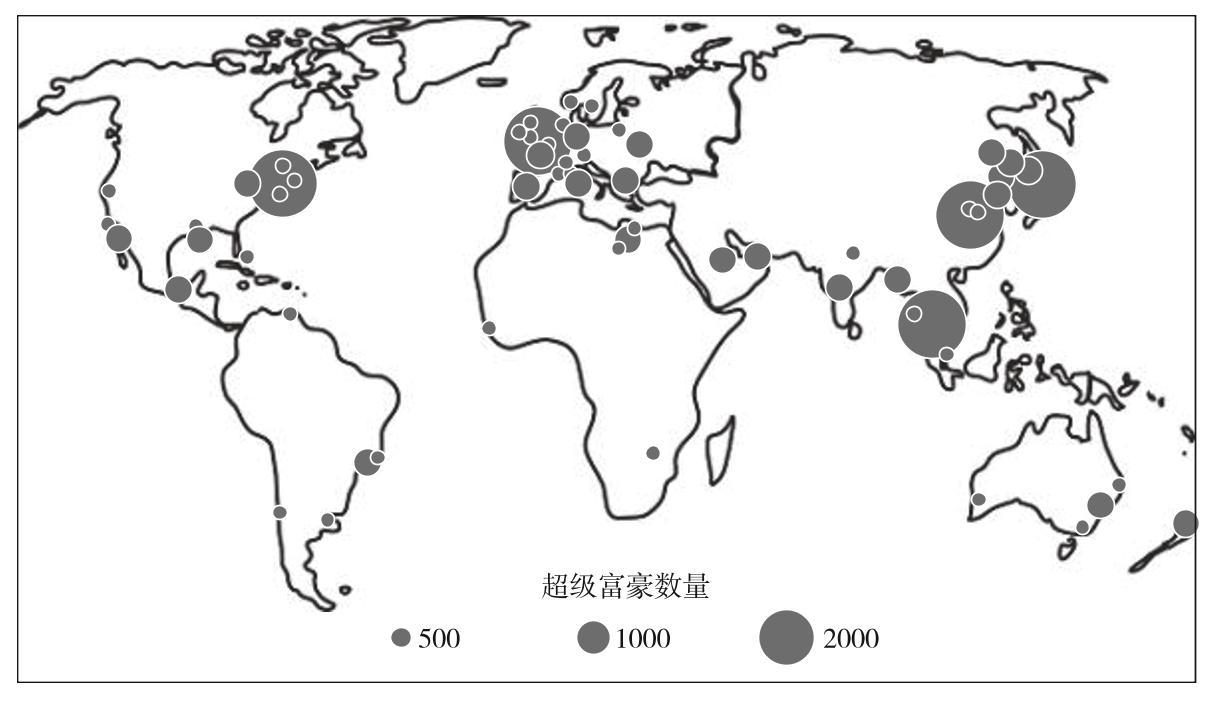
图3.2 超高净值人群的居住地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莱坊地产咨询公司,财富报告(2015),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注:超高净值人群,指购买的房屋价值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
10年前我并没有预料到如今科技创业公司和人才会向城市迁徙。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英特尔、苹果和谷歌等顶级科技公司把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微软把总部设在华盛顿雷德蒙德郊区,其他科技公司则聚集在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的郊区、奥斯汀郊区或者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带的办公园区。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和马丁·肯尼刚开始研究风险投资和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时,大部分获得风投资金的创业公司也设立在这些郊区。 [13]
后来,它们的地理分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流向城市中心。2012年,坐拥近65亿美元风投资金的旧金山都会区雄踞世界风投资金榜首,超过了拥有42亿美元风投资金的圣何塞地区(包括硅谷)和拥有超过20亿美元的纽约都会区,其中纽约地区的大部分风投资金集中在曼哈顿下城区。到2013年,旧金山都会区的风投资金量高达85亿美元,其中62亿流入旧金山市,圣何塞都会区为48亿美元,纽约都会区为30亿美元。 [14]
2013年,全美有54%的风投资金和57%的创业公司集中在城市地区。在旧金山湾区,60%的风投资金流向了适合步行的人口密集城区。在纽约,这一数字更是超过80%。在能够吸引全国各地风险投资的地区,通勤方式为步行、单车或公共交通的人数比例(16.6%)是全国平均水平(8.4%)的近两倍。另外,50%以上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共吸引了全美1/4以上的风投资金,超过30%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则吸引了全美1/3以上的风投资金。2013年旧金山市区有两个区域都有超过60%的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这两个区域各自吸引了超过10亿美元风投资金。
城市内的整体人口密度对科技创业公司扩大影响力和吸引风投资金至关重要,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高等教育的人口密度和创意阶层的人口密度,仅略逊于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这一吸引风险投资的最初因素。 [15]
虽然有一部分风投资金流入小城市或郊区,但它们也选择了最具城市特征的地带。硅谷的风险投资中心是帕洛阿托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汇集了超过15亿美元的风投资金。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风投资金规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远超过波士顿128号公路的沿线郊区。人口密集、适宜步行的圣莫尼卡吸引的风投资金规模也两倍于面积更大的洛杉矶。
科技初创企业向城市汇集的趋势也蔓延到了其他国家。金融中心伦敦以前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产业,如今却有数千个科技公司,创造了数万个科技就业岗位,创业公司每年获得超过8亿美元风投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西雅图和奥斯汀。 [16] 出现在全球风投资金和初创企业城市排行榜的前20名的非美国城市还有北京、上海、孟买、班加罗尔、多伦多、巴黎和莫斯科。另外,欧洲的柏林、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慕尼黑以及中东的特拉维夫和安曼的市中心也都出现了创业园区(见表3.1)。
表3.1 全球风险投资城市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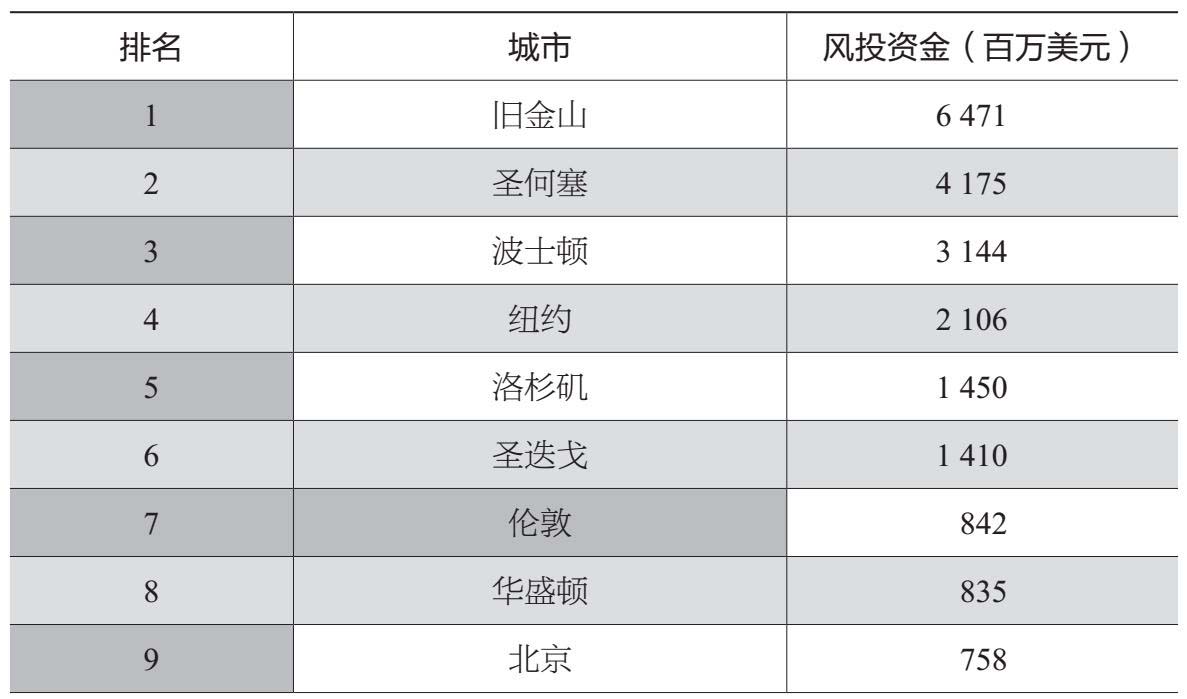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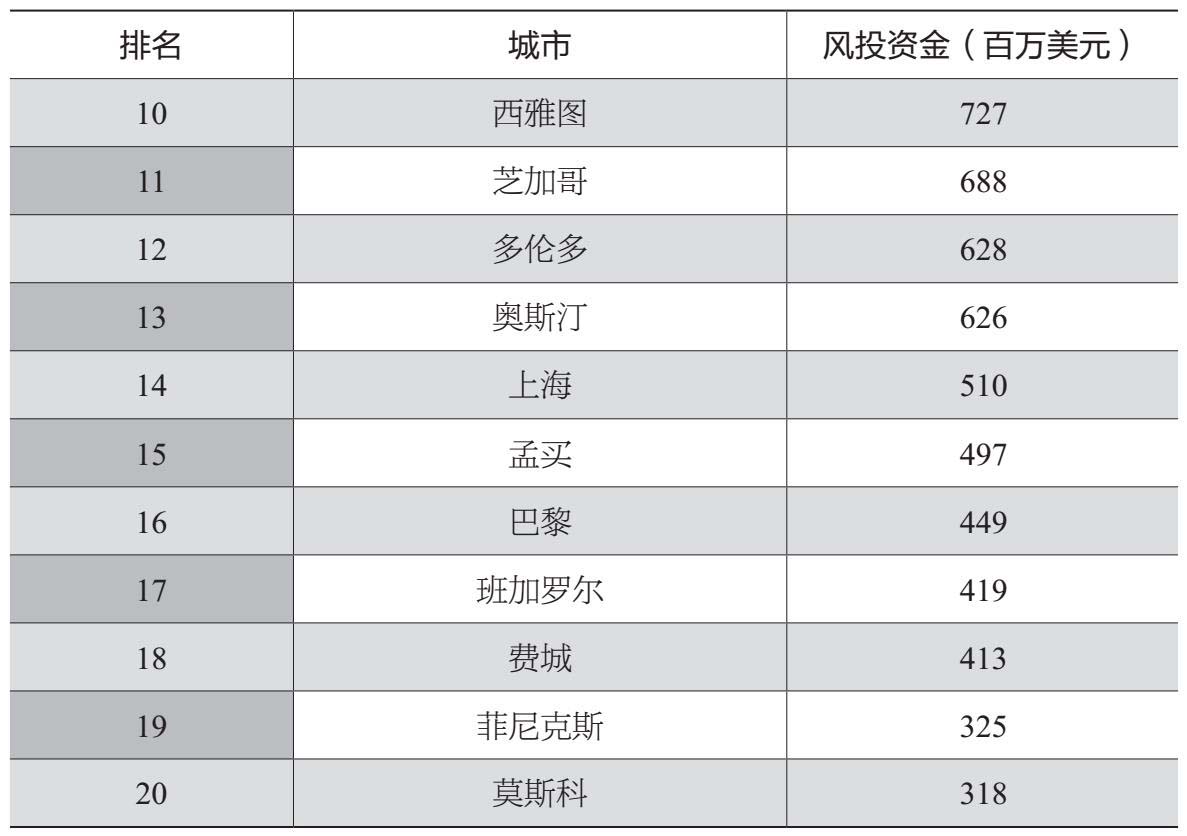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2012年汤森路透数据。
很多领先的创业城市本身也是世界主要超级城市。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顶端的纽约、伦敦和洛杉矶的风投资金规模在全球城市中分别位列第四、第七和第五。其他世界顶尖超级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北京和上海)也都在风投资金规模方面遥遥领先,科技风投资金规模榜单的前25名中有11个是全球超级城市。 [17] 创业公司在给城市带来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从超级城市中获得了发展动力。
创业公司和城市是天生一对。城市的多元开放、创新活力、文化丰富性和朝气蓬勃的街头生活,能为初创企业急需的新思想提供肥沃的孕育土壤。虽然微软、苹果和脸书等成熟大型科技公司的庞大总部还在郊区,但创业公司能对城市废弃工厂和仓库的建筑空间进行灵活改造并加以利用。
以前成功的创业公司往往专注于开发生产软件或硬件,廉价的郊区更能满足它们对大型设备和厂房的需求。而如今热门初创公司则涵盖数字媒体、游戏、手机应用等行业,城市才能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设计师、作曲人、编剧、音乐人和广告撰稿人。例如,汤博乐(Tumblr)和Buzzfeed(新闻聚合网站)为了贴近主流媒体和广告公司而设立在纽约。 [18] 有的创业公司则是为了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分别致力于改善城市交通和提高城市短期房屋租赁市场的效率。对这类创业公司来说,城市不仅是它们的诞生地,还是一个创新平台,它们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解决城市的问题。
大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对创业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纽约风险投资人弗雷德·威尔逊告诉我,一次他与电商平台Etsy的创始人罗布·卡伦会面时,发现卡伦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弹吉他。弗雷德称赞他是一名有天赋的音乐家,卡伦回答:“弗雷德,我确实是艺术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音乐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画家。而出生在这个年代,我的艺术就是做网站。”威尔逊补充说:“做网站需要科学技能,更需要艺术才华,而大部分的艺术家都集中在城市。” [19]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讨论过波西米亚主义价值观、丰富的文艺活动与科技创业公司发源地之间的联系。作为20世纪60年代迷幻乐的发源地,旧金山诞生了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杰弗森飞机(Jefferson Airplane)、大哥控股公司乐团(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爸爸妈妈乐队(The Mamas and The Papas)等音乐团体;西雅图出生的音乐人吉米·亨德里克斯对微软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影响极深,以至于后者在西雅图市中心专门建造了音乐体验计划博物馆,另外西雅图还是以涅槃乐队为代表的“垃圾摇滚”流派的发源地;奥斯汀也有其另类音乐流派,与科技产业一起成长发展;纽约和伦敦更是世界艺术文化的风向标。这些不是巧合,大城市创造和革新动力覆盖了各行各业。我的实证研究表明,文艺创新活动与科技产业、商业金融产业一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技向城市迁徙并非对历史偏差的急转弯式修正,早在2006年,著名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就提前察觉到未来风向的改变。他认为,虽然硅谷的优势不容小觑,但它也存在极大弊端,这个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行业发展天堂已经成了一个“巨型停车场”。他还写道:“旧金山和伯克利是好地方,但是它们在40英里 [01] 外,太远了。硅谷完全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绝佳的气候使它在所有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中鹤立鸡群,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会设法避免像硅谷一样在郊区大面积扩张。” [20] 他是对的,这一预言如今已得到应验。
然而也有不少人指责科技返回城市造成城市住房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2014年春天,奥克兰爆发游行,抗议矛头直指硅谷公司每天在奥克兰市区接送员工的班车。散发给班车乘客的传单上写着,“你们不是无辜受害者”“你们只图自己享乐,完全看不到你们周围那些贫穷、无家可归和与死亡苦苦斗争的人,因为金钱和成功已经迷住了你们的双眼”。几位抗议者甚至爬上一辆雅虎班车,其中一个人在巴士的挡风玻璃上吐口水。在旧金山米申区,抗议者打扮成小丑,带着健身球,排成金字塔阵形,在谷歌班车前跳大腿舞。
旧金山社会活动家和作家丽贝卡·索尔尼认为,这些班车就像“前来统治地球的外星霸主乘坐的宇宙飞船”。她写道:“一位享誉文坛40年、近期被提名为桂冠诗人奖候选人的杰出拉丁裔诗人,却在妻子接受化疗时被逐出住所,这可是他自成年后生活了整整35年的公寓啊!没人知道他会换个廉价公寓还是只能搬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没人知道这个已经容不下诗人的城市将走向何方。”在她眼中,湾区有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环保人士”,另一方是刚富裕起来的科技精英。然而艺术家有时也会被归入后者阵营,2016年,洛杉矶就爆发了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艺术家也是市中心的殖民者。 [21]
这类冲突在旧金山由来已久。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到过2000年旧金山针对L提案的“市场街角区战争”,这项提案主张限制旧金山市场街角区、教会区等市中心社区的科技行业发展和其他形式的绅士化发展,最后提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了。对旧金山绅士化发展的抗议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85年有评论家指出,“旧金山可能是全美国最绅士化的城市,10年前蓝领阶层的生活社区现在成了年轻专业人士的聚集地,这种变化催生了消费经济,著名连锁品牌大规模推销牛角面包,一些新词汇也随之产生:雅皮士化、牛角面包潮、曼哈顿化”。 [22] 在这场争夺城市空间的漫长战争中,科技初创企业和其从业人员只不过是最新出现的竞争者。
科技初创企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确实导致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提出此问题的不只是左派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中称创业城市和科技行业聚集地区为“不平等的制造者”,但他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发展的代价,“只要有人创业,就会有人变富;只要有人变富,就会出现财富不均等”。他继续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贫困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而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大部分时候只浮于表面症状而忽略了病因。 [23]
但是在房价上涨、不平等和绅士化问题上,城市的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应当负有多大责任呢?经验证据指向了不同的结论。科技公司的迁入毫无疑问推动了城市房价上涨,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城市尤为明显。房价与衡量创新能力、科技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指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度。
然而,经济不平等和城市科技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明确。一方面,科技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的聚集与工资差距的扩大息息相关,这很合情合理,因为收入差距反映了城市就业市场的分化,知识型雇员的收入远高于服务业人员和蓝领工人。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也反映城市科技行业发展和更广义的收入差距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两者没有明显的关联。在第五章中我将继续讨论两种形式的不平等——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两者的区别及其产生原因。就目前来看,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源头并非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而在于知识驱动型大城市具备的其他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最初吸引了科技公司及科技人员迁入城市。 [24]
其他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2015年,有研究者详尽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美国50个州的创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尽管创新与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上涨有密切联系,但与更广义范围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毫无关联。 [25] 事实上,创新水平越高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流动性也越高,人们更有可能进入比自己父母更高的收入层级。尽管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房价高昂,工资差距极大,但穷人和工人阶级也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旧金山市民和其他很多人其实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2014年4月对旧金山市民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人认为,科技行业从业者把其他人“挤出了城市”,降低了城市多元化,增加了城市排他性;但是近3/4(73%)的受访人相信,科技公司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超过一半(56%)的受访人认为,旧金山应该继续发展科技行业、提高对科技公司的吸引力。 [26]
随着科技行业的迁入,城市肯定会面临房价上涨压力,旧金山尤其如此。但科技行业也能带来革新、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科技行业不会让城市丧失活力,相反,它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对于遇到了真正问题的地方来说,把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当作替罪羊很方便,但阻挠科技向城市迁移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富人、科技和金融业的迁入引发了城市内部的剧烈冲突,给城市带来了挑战,但它们是否如一些批评家所言,削弱了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呢?结论是,并没有。事实上超级城市的创新优势反而加强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的经济复苏依靠的不仅是它在金融、银行和房地产行业的传统优势,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张。2003—2013年,纽约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13%的惊人增长。纽约市840万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6%,但它提供了美国8.6%的文化创意就业岗位(2003年这一数字是7.1%)。纽约汇集了全美28%的时尚设计师、14%的制作人和导演、12%的媒体编辑和12%的艺术指导 [27] ,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
大西洋对岸的伦敦在创意产业方面的主导优势甚至比纽约还耀眼。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2.5%,却拥有英国文化创意产业40%的就业岗位,其中约58%在电视、电影和广播行业,约43%在音乐和表演艺术行业。而且伦敦的文化优势还在扩大,2007—2014年间,伦敦为英国贡献了最大份额的创意产业就业增长。 [28]
超级城市规模庞大这一因素远不足以解释创意产业的集中程度之高。我们分析了美国创意经济的地理分布,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表演和舞蹈等,我们发现纽约和洛杉矶拥有的相关就业岗位数量远超其他城市,并且远超其城市的人口比例。 [29]
纽约和洛杉矶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先其他城市多少呢?很多。洛杉矶在艺术和创意领域的就业岗位占比是美国均值的近三倍,纽约的占比是均值的两倍多。其中,单看美术行业(包括画家和雕塑师)的就业占比,洛杉矶和纽约分别是美国均值的四倍和一倍半;在音乐人和歌手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是美国均值的逾两倍和三倍;在演员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十倍和两倍半;在制片人和导演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七倍和四倍半;在作家方面,两个城市均为美国均值的逾三倍;在时装设计师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八倍和十倍。 [30]
这两个超级城市之间当然也免不了一争高低。莫比曾在2014年说,他从纽约搬到洛杉矶是“因为创作需要能容忍失败的自由”,洛杉矶相对低廉的房租让失败没有那么可怕。他个人的经验之谈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离开纽约、前往洛杉矶的文艺创作者并不在少数。 [31] 然而,相较其他美国城市,洛杉矶和纽约还是傲视群雄。
图3.3展示了2010年美国部分城市在22个主要文艺产业的聚集度和就业数量,涵盖了视觉艺术、音乐、影视和设计领域。可以看出洛杉矶和纽约都十分突出,尤其是图中右上角的洛杉矶 [32] 。即便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它们的文艺产业聚集度和相关就业机会也远远领先其他美国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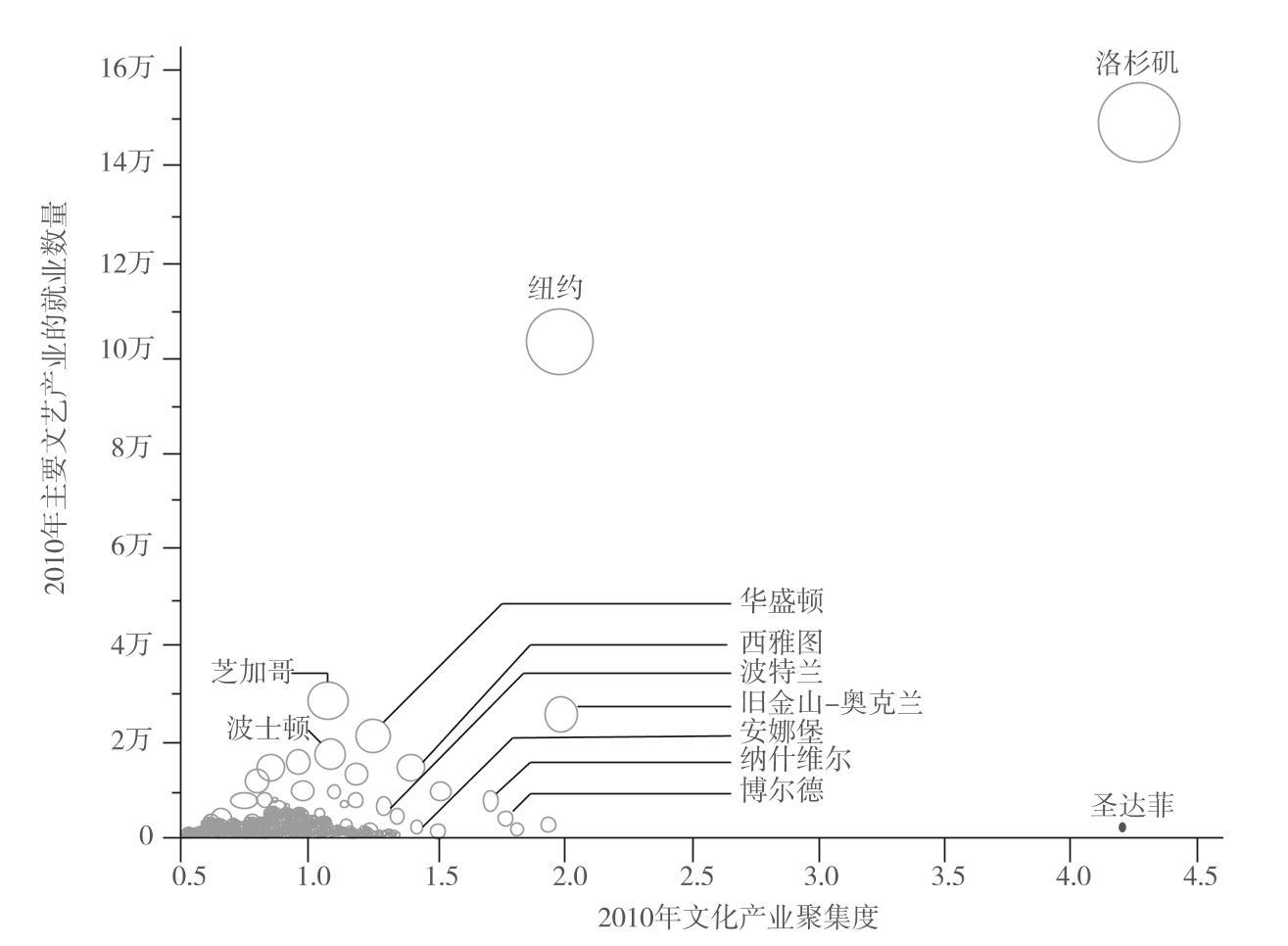
图3.3 赢者通吃的文化创新
资料来源:卡尔·格罗达赫、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妮科尔·福斯特以及詹姆斯·默多克,艺术人群的位置图:城市与小区级分析,城市研究51,No.13(2014):2822-2843。
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还能从流行音乐的视角观测这两大城市在创意产业的主导地位。过去几十年中,纽约和洛杉矶一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中心。实际上“赢者通吃”规则在流行音乐产业中体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金融、传媒和科技行业。通过对2007年十大流行音乐流派进行的地理分布研究,我们发现洛杉矶在其中六个流派中占领先地位,包括流行、摇滚、电子、拉丁、民谣和实验音乐;在三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包括都市、乡村和爵士乐。而纽约占领了爵士乐的榜首,并在摇滚、流行、电子、民谣和拉丁乐这五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只有两个——纳什维尔在乡村和基督教音乐中排名第一,亚特兰大在都市音乐这个流派排名第一。 [33]
20世纪的后50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法兰克·辛纳屈、猫王、披头士乐队,以及后来的碧昂丝、Jay-Z(说唱歌手)和泰勒·斯威夫特,纽约、洛杉矶和伦敦在这一时期三足鼎立。 [34] 1950年至今,约2/3(63.2%)的流行歌手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其中纽约占21%,洛杉矶占22%,伦敦占20%。当然,成名地不一定等同于出生地,据统计,分别只有14%、7%和2%的流行歌手出生在纽约都会区、伦敦市和洛杉矶市。披头士乐队在伦敦一举成名之前一直在英国利物浦和德国汉堡发展;著名美国本土音乐蓝调诞生于密西西比三角洲,在芝加哥发展成熟,后来才在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被大规模商业化;麦当娜搬到纽约之前住在底特律;麦莉·赛勒斯搬到洛杉矶之前住在纳什维尔郊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泰勒·斯威夫特先搬到纳什维尔,后搬到纽约;制作的热门单曲数量超过迈克尔·杰克逊的瑞典籍音乐制作人马克斯·马丁一直在洛杉矶有自己的工作室。现在这些城市可能不如从前那样适合事业刚起步的年轻音乐人和其他艺术家了,但它们仍是音乐人一夜成名、登上事业巅峰的风水宝地。
这三个城市为何如此杰出?原因之一是它们庞大的地理规模带来的巨型经济规模。它们不仅具备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还能将各行各业的人才技能汇集到一处——除了表演者和其他艺术家之外,还包括制作人、经纪人、作家、作曲人、舞蹈编导、设计师和工程师,这些都是文艺创作产业需要的。谁也不知道哪首歌能登上流行榜单,成功的永远是少数,通常要押注多次才能收获一次成功。而大型超级城市有最优秀的制作人、最完善的音乐发行支持系统和最快的新陈代谢体系,能在短时间内高效生产大量单曲,通过增加押注数量提高成功次数。另外,这些城市也是主流媒体的中心,而主流媒体在流行文化和造星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拥有发展完善的创意经济的城市很少见,这要求它们具备艺术、文化、技术和管理行业的综合实力。只有5%的美国城市(364个城市中的19个)拥有在各领域表现优异、功能完备的创意经济,其中包括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市和一些知识技术中心,如旧金山、圣何塞、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和奥斯汀。它们强劲多元的经济实力不仅限于创意、科技和管理行业,还体现在其他各个领域。 [35]
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过高的房价会抑制超级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但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没出现。2014—2015年,圣何塞都市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9%,超过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率2.5%的三倍,成为美国经济增速第二的城市。附近的旧金山在同期也创造了4.1%的经济增速。 [36] 由此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不但没有被削弱创造活力,还以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把其他地区远远甩在身后。
毋庸置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已成了最昂贵的地方,不再那么适合年轻贫穷的艺术家和音乐人生存,一些引领艺术发展的社区因此失去了创造活力。超级城市和技术中心的空间供不应求,它们有限的土地资源引来了激烈的竞争。
尽管资深音乐家和艺术家不断发出可怕的警告,但这几座城市的艺术创造力并没有被削弱,科技创造力还与日俱增。现在某些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还会怀念过去的好日子,感叹那个房租低廉、酒水便宜的创新天堂一去不复返,在我看来这颇具讽刺意味。虽然当看到昔日的朋克摇滚和新浪潮音乐先锋酒吧CBGB变成一家高档服装店时,我也感到很愤怒,但总体来说,现在这几座城市的创意经济比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多了。真有人希望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和洛杉矶的经济状况吗?我认为答案显而易见。新加入的科技行业让这些在文艺创新领域有传统优势的城市获得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坦率地说,关于城市变迁的某些激烈争论只是来自新城市精英群体内部的派系竞争,但是更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相对占优势的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穷人和工人阶层在城市蓬勃发展过程中被排挤、失去立足之地,但帮助他们的途径并不在于阻断财富创造的源头,而应是让经济发展更全面和富有包容性。
人们常把现在穷人和工人阶级面临的挑战框定为城市发展绅士化,绅士化可能已经成了现在有关城市话题中最大的焦点。虽然比起控诉超级城市的文化枯竭,或者把发达知识中心面临的问题全怪在科技行业头上,关于城市绅士化的讨论显得有理有据多了,但也有一些错误观念需要澄清。在下一章中我将对城市绅士化的问题展开讨论。
[1] David Byrne, “If the 1% Stifles New York’s Creative Talent, I’m Out of Here,” The Guardian, October 7, 2013,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07/new-york-1percent-stifles-creative-talent.
[2] 来自2010年史密斯和作家乔纳森·勒瑟姆在库伯联盟学院的对话,参见See Jeremiah Moss, “Find a New City,” Jeremiah’s Vanishing New York, May 3,2010, http://vanishingnewyork.blogspot.ca/2010/05/find-new-city.html。
[3]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Because Creativity Requires the Freedom to Fail,” The Guardian, February 3, 2014,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feb/03/leave-new-york-for-los-angeles.
[4] 参见Scott Timberg, Culture Crash: The Killing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arah Kendzior, “Expensive Cities Are Killing Creativity,” Al Jazeera, December 17, 2013, 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3/12/expensive-cities-are-killingcreativity-2013121065856922461.html.
[5] Marcus Fairs, “London Could Follow New York and Lose Its Creative Class Warns Rohan Silva,” Dezeen, July 10, 2015, www.dezeen.com/2015/07/10/creative-people-designers-new-york-move-los-angeles-cautionary-talelondon-warns-rohan-silva; Alex Proud, “‘Cool’ London Is Dead, and the Rich Kids Are to Blame,” The Telegraph, April 7, 2014, 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10744997/Cool-London-is-dead-and-the-rich-kidsare-to-blame.html.
[6] 从统计学上来说,对于这三个群体——商业金融人士、科技人员和其他创意工作者——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而对于服务业人员来说这两者则呈负相关的关系。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的关系如下:商业金融人士(0.6);科技人员(0.44);画家、音乐家及其他文化创意工作者(0.42)。美国劳工局统计的文艺创意工作者的数据只适用于把创意工作登记为自己主要职业的人,不包含主业为其它职业的贫困或年轻艺术家。虽然我们容易对这种还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有抱负的艺术家另眼相待,但其实很多其它行业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得到自己的理想工作之前,也可能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
[7] 关于伦敦,参见Jonathan Prynn, Mira Bar-Hillel, and Lindsay Watling,“London’s £3bn Ghost Mansions: ‘Foreign Investors Are Using Capital’s Finest Homes as Real-Life Monopoly Pieces,’” Evening Standard, February 14, 2014, www.standard.co.uk/news/london/londons-3bn-ghost-mansionsforeign-investors-are-using-capitals-finest-homes-as-reallife-monopolypieces-9128782.html. 关于纽约,参见Sam Roberts, “Homes Dark and Lifeless, Kept by Out-of-Towner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1, www.nytimes.com/2011/07/07/nyregion/more-apartments-are-empty-yet-rentedor-owned-census-finds.html; Julie Satow, “Pieds-A-Terre Owners Dominate Some New York Building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4, www.nytimes.com/2014/10/26/realestate/pieds-terre-owners-dominate-some-newyork-buildings.html。
[8] 关于伦敦的外国购房者,参见Patrick Worrall, “FactCheck: Are the SuperRich Killing ‘Cool London’?,” BBC Channel 4 Fact Check Blog, April 14, 2014, http://blogs.channel4.com/factcheck/factcheck-superrich-drivingproperty-prices/18073. 关于On the displacement of established London elites by the global super-rich, see Luna Glucksburg, “Is This Displacemen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Super-Gentrification in London’s Alpha Territ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IBG)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London, August 31, 2016. “寡头统治化(oligarchification)”一词来自Feargus O’Sullivan, “No One Feels Sorry for the Latest Victims of London’s ‘Gentrification,’” CityLab, September 2, 2016, 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9/the-latest-victims-of-london-gentrification-are-therich/498536。
[9] Louise Story and Stephanie Saul, “Stream of Foreign Wealth Flows to Elite New York Real Esta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www. nytimes.com/2015/02/08/nyregion/stream-of-foreign-wealth-flows-to-timewarner-condos.html; “Story and Saul: The Hidden Money Buying Condos at the Time Warner Cent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www.nytimes.com/2015/02/08/nyregion/the-hidden-money-buying-up-newyork-real-estate.html; Octavio Nuiry, “Are Foreigners Stashing Billions in U.S. Real Estate?” Housing News Report, September 2015, https://issuu.com/ftmagazine/docs/housingnewsreport_sept; Saskia Sassen, “Who Owns Our Cities—and Why This Urban Takeover Should Concern Us All,” The Guardian, November 24, 2015,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nov/24/who-owns-our-cities-and-why-this-urban-takeover-should-concern-us-all.
[10]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1899)].
[11]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Isabel Ritchie, The Geography of the Global Super-Rich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The-Geography-of-the-Global-Super-Rich.pdf. 我们的图是基于福布斯对全球1826名亿万富豪的统计数据,这些亿万富豪只占全球人口的0.00003%,但坐拥七万亿美元的资产,大概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的10%。亿万富豪的人数和净身家和人口数量正相关(0.41,0.33),与经济产出正相关(0.68, 0.61),与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正相关(0.47, 0.49),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也正相关(0.49, 0.52)。虽然亿万富豪多住在超级城市,也有亿万富豪仍住在他们发家的较小城市,例如,沃尔玛家族住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沃伦·巴菲特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12] Knight Frank, The Wealth Report—2015, 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13] 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Financed Innovation in the U.S.,” Research Policy 17 (1988): 119–137; Richard Florida and Donald Smith, “Venture Capital Formation,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no. 3 (September 1993): 434–451.
[14] Richard Florida, “The Joys of Urban Tech,”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2012,www.wsj.com/articles/SB10000872396390444914904577619441778073340;Richard Florida, “The Urban Tech Revolution,” Urban Land, October 7, 2013,http://urbanland.uli.org/economy-markets-trends/the-urban-tech-revolution;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Rise of the Startup City: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City-CMR-FINAL-formatted.pdf.
[1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venture-capital-goes-urban;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 (Toronto: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 风险投资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是0.55,与大学毕业生的相关系数是0.50,与创意阶层的相关系数也为0.5。比人口密度相关系数更高的只有科技行业聚集度,这是风投需求最早诞生的地方。附录的表1提供了详细数据。
[16] Max Nathan, Emma Vandore, and Rob Whitehead, A Tale of Tech City: The Future of Inner East London’s Digital Economy (London: Centre for London, 2012).
[17]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
[18] Alessandro Piol and Maria Teresa Cometto, Tech and the City: The Making of New York’s Startup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Mirandola Press, 2013).
[19] “Stern’s Urbanization Project Hosts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Florida and Fred Wilson,” 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October 9, 2013, www.stern.nyu.edu/experience-stern/news-events/conversation-florida-wilson.
[01] 1英里约为1609米。——编者注
[20] Paul Graham, “How to Be Silicon Valley,” PaulGraham.com, May 2006,www.paulgraham.com/siliconvalley.html.
[21] Rory Carroll, “Oakland: The City That Told Google to Get Lost,” The Guardian, February 11, 2014,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feb/10/city-google-go-away-oakland-california; Ellen Huet, “Protesters Block, Vomit on Yahoo Bus in Oakland,” SFGate, April 2, 2014, http://blog.sfgate.com/techchron/2014/04/02/protesters-block-vomit-on-yahoo-bus-inoakland; Rebecca Solnit, “Diary: Google Invad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7, 2013, 34–35, www.lrb.co.uk/v35/n03/rebecca-solnit/diary. 关于洛杉矶市中心爆发的当地人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参见Jennifer Medina, “Gentrification Protesters in Los Angeles Target Art Galler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6, www.nytimes.com/2016/11/05/us/losangeles-gentrification-art-galleries.html。
[22] Dan Morain, “Gentrification’s Price: S.F. Moves: Yuppies In, the Poor Ou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 1985,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85-04-03/news/mn-28445_1_san-francisco-s-skyline.
[23] Paul Graham, “Economic Inequality,” PaulGraham.com, January 2016,http://paulgraham.com/ineq.html.
[24] 夏洛塔·梅兰德和我调查了城市科技行业的关键指标(初创公司的数量,风险投资规模,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等)与住房负担和不公平的关系。月住房支出中位数与创新能力(0.49)、高科技行业聚集度(0.58)、风投初创公司(0.60)和投资规模(0.56)密切相关。薪资不公平与创新能力(0.44)、风投初创公司(0.60)和风险投资规模(0.55)也有正相关的关系。参见附录表1。
[25]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tonin Bergeaud, Richard Blundell, and Davi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2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247.
[26] Aki Ito, “San Franciscans View Tech Boom as Benefit at Cost of Diversity,”Bloomberg, April 4, 2014, www.bloomberg.com/news/2014-04-04/sanfranciscans-view-tech-boom-as-benefit-at-cost-of-diversity.html.
[27]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Rosemary Scanlon, and Steven Pedigo,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July 2015,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Richard Florida, “Resetting and Reimagining New York City’s Economy,” CityLab, July 29,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7/resetting-and-reimagining-new-york-citys-economy/399815; Adam Forman,Creative New York,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June 2015, https://nycfuture.org/research/publications/creative-new-york-2015.
[28] Juan Mateos-Garcia and Hasan Bakhshi, The Geography of Creativity in the UK, Nesta, July 2016, www.nesta.org.uk/sites/default/files/the_geography_of_creativity_in_the_uk.pdf. Greater London here is defined as its “Travel to Work Area,” or TTWA.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evin Stolarick, “Geographies of Sc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ertainment, 1970–2000,”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 no. 1 (2012): 183–204.
[30] 这些数据是基于一个叫“区位商”的指标,该指标用某项经济活动在一个城市地区的产值比重除以它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实际区位商数值如下:对于创业行业整体来说,洛杉矶为2.7,纽约为2.2;对于艺术家来说,洛杉矶为3.8,纽约为1.5;对于音乐人和歌手来说,纽约为2.7,洛杉矶为2.2;对于制作人和导演来说,洛杉矶为6.7,纽约为4.6;对于作家来说,纽约和洛杉矶都为3.3;对于时尚设计师来说,纽约为9.9,洛杉矶为7.7。以上均为2014年的数据。
[31]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Charlynn Burd, “Metropolitan Migration Flows of the Creative Class by Occupation Using 3-Year 2006–2008 and 2009–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ata,” Journey to Work and Migration Statistics Branch, Social, Economic, and Housing Statistics Division (SEHSD), US Census Bureau, Working Paper no. 2013-11,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Los Angeles, April 9–13, 2013.
[32] Carl Grodach, Elizabeth Currid-Halkett, Nicole Foster, and James Murdoch,“The Location Patterns of Artistic Clusters: A Metro- and NeighborhoodLevel Analysis,” Urban Studies 51, no. 13 (2014): 2822–2843.
[33] 基于MySpace网站的数据,原始数据由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希尔弗和芝加哥大学的文化政治中心所整理,我是在2007年初这个网站最火的时候下载的(当时它的访客数量超过了谷歌),数据覆盖了300多万名音乐人。因为当时MySpace的线上覆盖面极广,它能很好地记录数字环境下地点对于流行音乐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我在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清理,并根据音乐流派和地点分类,最后得到的可用数据覆盖200多万名音乐人,横跨十个音乐流派:摇滚乐、城市音乐、流行乐、电子乐、民谣、乡村音乐、基督教音乐、拉丁与加勒比黑人音乐、实验音乐和爵士乐。为了找到对流行乐影响力最大的地点,我们结合粉丝数、观看数和累计播放量创造了一个综合指标:音乐流行度指数。参见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America’s Pop Music Entertainment Complex,” CityLab, May 28, 2013, www.citylab.com/design/2013/05/geography-americas-pop-musicentertainment-complex/5219。
[34]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Pop Music Superstars,” CityLab,August 27, 2015, www.citylab.com/tech/2015/08/the-geography-of-popmusic-superstars/402445.
[35] Shade Shutters, 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这项研究指出,其他城市要进入这个精英城市俱乐部非常困难,首先必须要在所有方面表现出色,产业构成和人才库必须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创新性来推动经济发展。另外,它还要克服阻碍创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如高房价和高居住成本,持续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城市地区能满足这些要求。
[36] Jessica Floum, “Bay Area Economy Outpaces the US, Chin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6, 2016, 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BayArea-economy-outpaces-U-S-China-9289809.php.
2014年2月的“黑人历史月”活动中,《为所应为》和《黑潮-麦尔坎》的导演斯派克·李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普瑞特艺术学院发表演讲。提问环节中听众向李提了一个有关绅士化的问题,他回答:“你如果在凌晨3点的第125街上看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白人妈妈,肯定会觉得不对劲。”这位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导演就这个话题谈了很多,他强调绅士化不是社区的变化,而是人的变化,新殖民主义土地掠夺已经不足以形容绅士化了,他称之为“混账哥伦布综合征”。 [1]
李认为绅士化就是富白人把穷黑人赶出自己原来的家园,他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一直以来就有很多评论家批评绅士化就是富有开发商大量购入土地和楼房,并将原来的居民挤走的剥削行为。 [2]
绅士化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情感问题(鉴于此前我受到的谴责,我应该清楚这一点 [3] )。很多新来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愧疚感,因为他们的迁入改变了社区样貌,还可能使有些邻居被迫搬走。用2014年一篇文章的话说:“你基本不可能不当绅士化者。” [4] 老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有很深的感情,当他们看到富裕的陌生人迁入,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时,即使自己没有被迫搬走,心里也不是滋味。人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居所,也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居住权利,否则就会激发矛盾。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对绅士化的批评有言过其实之嫌。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兰斯·弗里曼对纽约哈林区和其他社区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很多人担心富裕的绅士化者会直接取代贫困的原住居民,但这并不是事实。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道格拉斯·马西是研究种族和经济分化问题的顶尖专家,他认为,比起规模更大的城市人口流动,绅士化的影响不过是“九牛一毛”。他还认为某些反对绅士化的城市专家十分虚伪,“自由派城市专家一面谴责白人抛弃城市,造成美国的郊区化,一面又称极少数重返城市的白人精英为投机分子,批评他们造成市中心的绅士化”。 [5]
在本章中我将着眼于事实,力求为绅士化的讨论提供客观视角。自2000年起,随着大规模返城浪潮的兴起,绅士化进程也加快了。不过到目前为止,绅士化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几个顶尖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尽管大量研究表明,被绅士化直接挤出城市的人并不多,但重返城市的浪潮全面推升了城市房价,而饱受其害的就是贫困人口。媒体对绅士化的过度关注让人们忽视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长期集中的城市贫困。客观地理解绅士化十分重要,因为它是理解新城市危机根源的前提。
一般来说,绅士化是指社区价值增长和富人、白人、年轻居民占比升高的过程。露丝·格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了这个名词,用来描述伦敦工人阶级社区向中产和上流绅士社区的转变。她写道:“‘绅士化’一旦开始,便会迅速发展,直到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人阶层都搬走,整个社会的特质都改变了。” [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绅士化有两种主要的存在方式。格拉斯指出,第一种方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逐渐搬回以前的高端居民区,比如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波士顿的灯塔山、费城的社会山或者华盛顿的乔治敦等。1970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地主》(The LandLord )就描绘过这种绅士化的方式,影片中博·布里吉斯扮演的纨绔子弟用自己继承的遗产购买了贫民窟的一处公寓,他想赶走黑人租客并把公寓楼翻修成自己的私人别墅(当然故事后来发生了意外转折)。电影取景于布鲁克林的公园坡社区,当年的公园坡还破败不堪。这部电影虽然是当年的票房毒药,但它准确地预言了公园坡社区后来的经济和种族发展状况。 [7]
一项对这种绅士化方式的早期研究调查了华盛顿的两个社区。 [8] 第一个是处于过渡期的芒特普莱森特社区,有很多亟待翻修的破旧住宅楼,常驻居民的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社会阶层状况十分多元化。但新迁入的绅士化者大多是年轻单身男性,他们喜欢这里历史悠久而有趣的建筑,愿意接受社区的高犯罪率。第二个是绅士化程度更高的国会山社区,多数建筑已经翻新过了,离居民的工作地也很近。它吸引了不同类型的绅士化者,除了单身男性外,还有较年长的居民、已婚或未婚的女性以及有孩子的家庭。相对于芒特普莱森特社区的单身男性,这里的新迁入者更倾向于长居,他们对社区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也更多地投资于社区的未来发展。新来者挤出老居民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国会山社区尤甚,而黑人、其他少数族裔和老人受到的影响最严重。这项研究警告决策者应关注这一趋势。
第二种绅士化方式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对旧工厂和仓库的再改造利用。随着工业迁往郊区,艺术家、音乐家和设计师开始把废弃的旧工厂和仓库改造成工作室和表演场地。包括极简艺术家唐纳德·贾德在内的很多艺术家都是在曼哈顿下城的阁楼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阁楼周围有很多俱乐部和酒吧,包括Café Wha酒吧、马德俱乐部(Mudd Club)和CBGB酒吧等都曾经为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大卫·拜恩和雷蒙斯乐队提供了磨炼自己、最终被星探发现的场所。
绅士化已经存在数十年了,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心它会对社区和城市造成危害。在1981年,有位专家提出要警惕绅士化给旧金山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所说的与我们今天听到的很相似,“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以后只有精英才住得起旧金山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罗森对《纽约时报》说:“在未来10年,除非我们采取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否则所有的中等收入群体都会被挤出他们原来生活的社区。旧金山会变成一个极其昂贵的生活地区,这里只有富有的单身人士、退休人员和在金融区工作的高管,而不富裕的人将很难在这里立足。” [9]
如果把城市绅士化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里审视,就更容易看明白社区在漫长岁月里是如何变迁的。社区从居民区变成工商业中心,再变回居民区,从富裕变贫困,再变富裕。社区变迁的过程可能很痛苦,但这是城市的自然特征。城市就是永不停歇的施工区,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和阶级构成也在改变。虽然从外表上看建筑可能没什么变化,但建筑里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
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他的学生在2014年的研究中追踪了纽约苏荷区格林尼街的一段仅长486英尺 [01] 的街区在三个多世纪里的发展史,说明了城市社区建立和重建的过程。 [10] 1641年,荷兰殖民者把这块土地作为农场特批给被解放的非洲黑奴,作为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缓冲地带。荷兰人离开之后,社区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价值也随之升高,很快就被一个更大的农场合并。大农场后来在18世纪末破产。到19世纪初时,这里开始出现时尚的联排别墅,在曼哈顿南部港口和金融区工作的商人和银行家纷纷迁入。黄热病暴发后,格林尼街上最富裕的居民纷纷迁往纽约市北部。到19世纪中期,这里的住宅和酒店变成了妓院。
城市工业化开始后,格林尼街社区再次转型。19世纪90年代,除了两栋老房子之外,几乎所有原来的建筑都被拆除,人们建起了五六层高的仓库和工厂,格林尼街成了纽约服装贸易中心,尤以制帽出名。到1911年,位于格林尼街和华盛顿广场拐角以北六个街区的三角内衣工厂发生大火灾,社区命运再次被改写。因为这里的建筑开始无法上保险,服装产业和此前的红灯区一样向上城迁移。此后格林尼街又被废弃了一段时间,只在罗伯特·摩西提出改造曼哈顿下城,将其变成多条高架快速公路贯穿的柯布西耶风格的超级街区时,这个社区才重新引起公众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家迁入社区废弃的工业楼,而现在这些艺术家正在被高档商店和高端住宅挤走。伊斯特利研究中展示的详细房地产价格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左右——也就是此轮绅士化的发展时期,该社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房地产价格增长。
由于返城浪潮加速和超级城市房价暴涨,现在城市绅士化比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富争议性。1990—2014年,美国前100的大城市中有超过一半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获得了人口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相比之下,从1970—1980年,同样的前100的大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获得了人口增长。 [11] 社会上层人士、富人、高学历人群和白人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的再城市化发展。房地产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的数据显示,2000—2014年,美国收入前10%的家庭最有可能搬回城市人口密集社区。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和丹佛,高收入群体返回城市现象最为显著,其他城市也有类似趋势。同时,城市里的较底层的居民则被迫迁出。还是2000—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最有可能离开城市。 [12]
年轻人在绅士化进程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规划师马库斯·穆斯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术语——“青年化”。他的调查显示,曼哈顿的大片社区、布鲁克林邻近曼哈顿的社区,以及芝加哥、多伦多和旧金山的市中心都被年轻人占据了。在过去10年的美国前50大城市中,市中心的年龄在25~34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口增长速度是郊区同类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这些市中心社区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口数量增长占全国的25%。尽管如此,重返城市浪潮中人数最多的不是出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00年的“千禧一代”,而是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X世代”,他们中最年轻的现在也快40岁了。因为年轻人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普遍推迟,所以他们能在市中心住更长时间。如今城市里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单身群体和没有孩子或孩子还小的夫妇。但是不管怎么划分,重返城市的都是年轻人中的优势群体。 [13]
绅士化和返城浪潮中,不仅有富裕白人的驱动,还有黑人中产阶级的身影。一份针对1500个城市社区的调查显示,1990—2000年,新迁入的高学历黑人家庭贡献了社区收入增长的1/3。城市社区对黑人中产阶级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为了避免歧视,普遍不愿搬去郊区。由于郊区长期存在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黑人中产阶级和黑人上层人士比同阶层的白人更多地聚集在城市中心。他们被高房价挤走时,则倾向于搬到条件更差的黑人社区,从而将那些社区绅士化了。 [14]
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纳撒尼尔·鲍姆-斯诺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同事丹尼尔·哈特利对近几十年的城市绅士化进行了深层研究。他们通过追踪1970—2010年间美国120个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距离中心商业区不足3英里)的变迁 [15] ,形成了三大研究要点,能帮助我们理解绅士化的驱动力及识别这场博弈中的赢家和输家。
第一,城市绅士化是一个较近时期出现的现象,自2000年后蔓延速度急剧加快。从1980—2000年,市中心社区居民主要以穷人和黑人为主,城市绅士化只发生在有限的几个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一时期的人们不论收入高低,都在离开城市,其中也包括受过教育的白人和工人阶层白人。2000年后,人们开始重新搬回城市,情况发生了急剧改变。
第二,返城浪潮的主力军是高收入和高学历的白人。在1980年,只有纽约和圣塔芭芭拉两个城市的市中心及其周边社区聚集了众多高收入、高学历白人。但自2000年之后,他们开始大规模重返市中心。到2010年,华盛顿、芝加哥、休斯敦和亚特兰大等城市的市中心都迁入了大量高收入、高学历白人。在该研究覆盖的城市中,居住在市中心的高收入、高学历白人家庭比例在2000—2010年上升了约2/3。
吸引他们重返城市中心的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高薪的知识、专业、技术和创意类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二是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可以缩短上下班通勤时间。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城市提供的设施——图书馆、博物馆、餐厅和咖啡店。简而言之,这些高收入白人群体通过住在市中心可以缩短上下班通勤时间、靠近高薪工作机会并获得享受城市设施的特权。
第三,随着优势人群的迁入,低收入、低学历的少数族裔离开,或者说被挤出了社区,主要是因为无力承担高住房成本。低收入人群的迁出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市中心会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设施,能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和经济流动性。弱势人群被挤出市中心后集中在衰败的郊区和城市中偏远和不发达的社区,其结果就是不平等和空间隔离问题不断加剧。我将在第六章到第八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总之,城市绅士化远非某一类人群自身的意愿和选择,不论是如今重返城市的年轻人、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占领阁楼的艺术家。它是更广泛因素的产物,如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这些因素影响了个人选择,也改变了城市和社区的发展轨迹。 [16]
举例来说,公共交通的地理分布长期影响着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个世纪前,有轨电车的线路影响了早期郊区的分布。 [17] 而今天富人们纷纷迁入公共交通线路沿线社区,公共交通进一步刺激了绅士化发展。具体来说有两种刺激方式。一方面,对公共交通的大规模投资象征着对社区转型的大力投入,从而吸引了更多富裕居民,提高了房地产价值。另一方面,公共交通能帮优势群体缩短通勤时间,高学历专业人士现在更愿意支付溢价来住在市中心的工作地点附近或车站附近。 [18] 这种发展趋势还会自我加强。当越来越多富裕家庭住在交通线路和换乘站附近时,这些社区的房价就会升高,优质的公共设施也随之而来。而更多更好的商店、咖啡馆、餐厅、学校、公园以及其他的设施又提高了社区吸引力,进一步抬高房价。公共交通线路周围的社区的绅士化反映了一种稀缺性:公共交通沿线社区不动产价格高企,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多的公共交通资源和交通便利的社区。
公共交通只是刺激绅士化的众多公共投资中的一种,学校也是一例。以前,高犯罪率和低教育质量的学校曾一度令中产阶级家庭离开城市。最近几十年,随着新的特许学校和更有吸引力的学校的出现和老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富裕家庭决定重返城市,甚至是才刚有孩子的家庭也愿意留下来。当城市社区中的优势群体到达一定数量后,来自他们的政治压力又为当地学校争取到了更多投资。
另一项吸引高学历和高收入居民重返城市的公共投资渠道是高校及其附属医疗中心,即所谓的“教育与医疗”。公立大学与私立研究型大学都能获得联邦政府的大额资助,很多学校为教职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补贴,这类人群往往就住在学校附近的社区,给这些社区带来了绅士化。
给公园和绿地的公共投资也刺激了绅士化发展。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沿线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住宅开发项目。公园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是社区发展的象征。从纽约的哈德逊城市广场、多伦多的湖滨区改造到匹兹堡北区的城市体育场,享受高额政府补贴的城市改造项目用纳税人的钱把老工业区改造成复合型开发区,吸引专业人士和新市民,也让邻近社区开始了绅士化进程。
不过讽刺的是,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的迁入让城市变得更像郊区。现在的新型城市公寓楼提供一系列类似郊区的公共设施,比如葡萄酒储存区、家庭影院、健身房、露天平台、户外游泳池和停车场。在一栋位于纽约市切尔西区十一大道的高端公寓楼里,居民可以用电梯把车停到家门口。城市中绅士化社区的郊区化也体现在占地空间上,今天的城市居民占地面积几乎和郊区居民一样大。城市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是1678平方英尺,而郊区家庭平均为1800平方英尺。平均到个人的话,城市居民为767平方英尺,仅略低于郊区居民的800平方英尺。城市中崭新的改造建筑和宽敞的空间正在让拥挤脏乱的居所成为过去时。
尽管绅士化在全国范围广泛存在,但在昂贵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情况则更为严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2000—2007年,美国前55大城市中有3/4的城市的绅士化社区不足10%,有40%的城市的绅士化社区不足5%(研究中将绅士化社区定义为,在2000—2007年间,房价从价格分布图下半部分上升到上半部分的社区 [19] )。根据这个衡量标准,只有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西海岸的旧金山、波特兰和西雅图等少数几个城市存在大规模绅士化现象(见图4.1)。
我的团队把经济、社会和人口方面的关键指标与上述的研究数据一起分析,发现绅士化出现在特定的发达城市。绅士化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富裕程度、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和科技专家、文艺工作者和大学生的人数占比呈正相关。绅士化还与公共交通的使用呈正相关,与城市扩张呈负相关(城市扩张用独自开车上下班的人数比例衡量)。 [20] 也就是说,正是知识中心和超级城市的专属特征孕育了城市化。与其说绅士化是普遍的城市特质,不如说它是成功城市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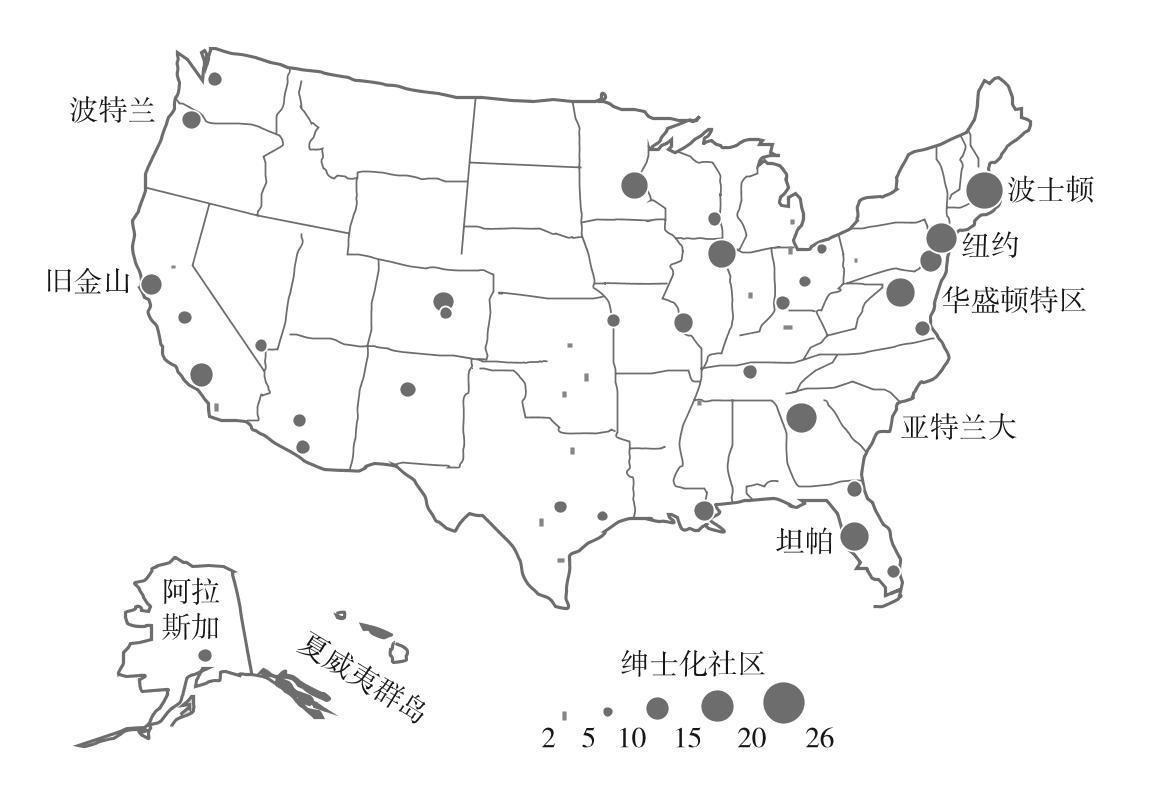
图4.1 大城市的绅士化差别很大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源于丹尼尔·哈特利的《绅士化与金融健康》(Gentrification and Financial Healt ),以及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2013。
可以说,正是因为绅士化主要发生在超级城市,它才从最开始就吸引了广泛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都在超级城市生活和工作。今天有1/5的新闻工作岗位集中在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而在2004年这一比例只有1/8(新闻业在超级城市的聚集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行业)。 [21] 新闻工作者自然会报道自己所在城市发生的绅士化现象,不过这些报道可能存在微妙的偏见。一项2015年的研究找出了《纽约时报》在1980—2009年间报道过的所有绅士化社区,包括已经绅士化的和正在发生绅士化的社区,并把它们与更详尽的研究(比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研究)所定义的绅士化社区进行对比。 [22] 结果发现,《纽约时报》更倾向于把绅士化限定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边界的社区,而不是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新闻工作者或艺术家更容易看到发生在自己社区的绅士化现象,这种偏见会让大家忽视某些重要事实。
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绅士化也集中于部分特定区域。纽约大学弗曼中心在2016年的研究表明,纽约的绅士化社区占比仅略高于1/4。 [23] 研究人员研究了纽约市55个社区从1990—2014年的演变,发现只有占比27%的15个社区能被算作绅士化社区,即期初收入低于中位数的40%,但研究区间的租金增长高于中位数的社区。占比13%的7个社区被归为未绅士化社区,一直维持贫困状态。占比60%的32个社区被归类为高收入社区,即期初收入就高于中位数的60%。高收入社区不一定很富裕,但一直属于中产阶级社区。另外,未绅士化社区往往紧挨着绅士化社区,在曼哈顿上城和布鲁克林的部分地区尤为明显,正是这种集中优势和集中弱势毗邻而居的现象定义了今天的城市(见图4.2)。
弗曼中心的调查表明,在过去20多年里,纽约市的不同地区租金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1)。威廉斯堡和绿点区的租金增长最快,高达79%;哈林区中心、下东区和唐人街的租金增长超过50%;哈林区东部和布什维克区的租金增长超过40%;贝德福德-斯图文森、晨边高地、汉密尔顿高地的租金增长超过36%;而皇冠高地南部的租金增长仅略高于18%,布朗斯维尔和海洋山丘的租金增长略高于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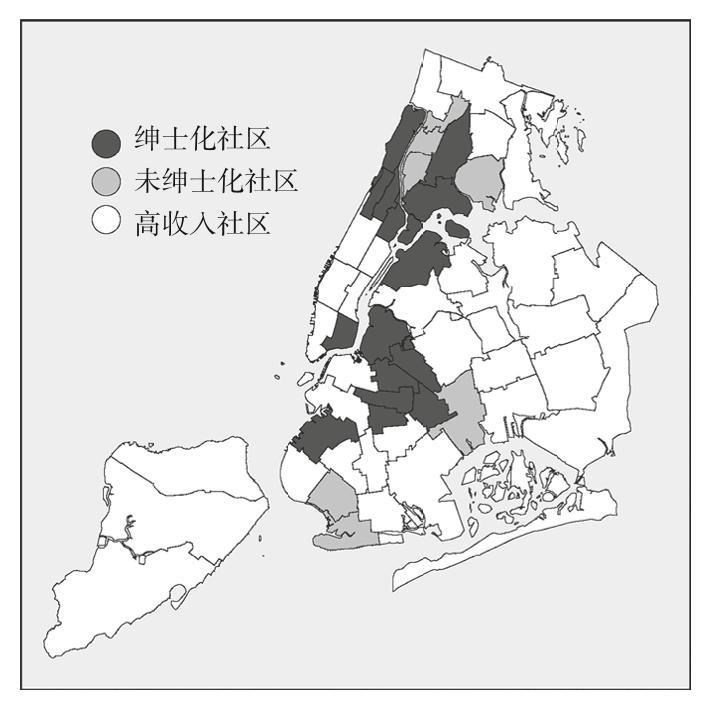
图4.2 纽约市的绅士化社区与未绅士化社区分布
资料来源:纽约大学弗曼中心,《2015年纽约市住房和社区状况》(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2016年5月。
表4.1 纽约绅士化社区的房租增长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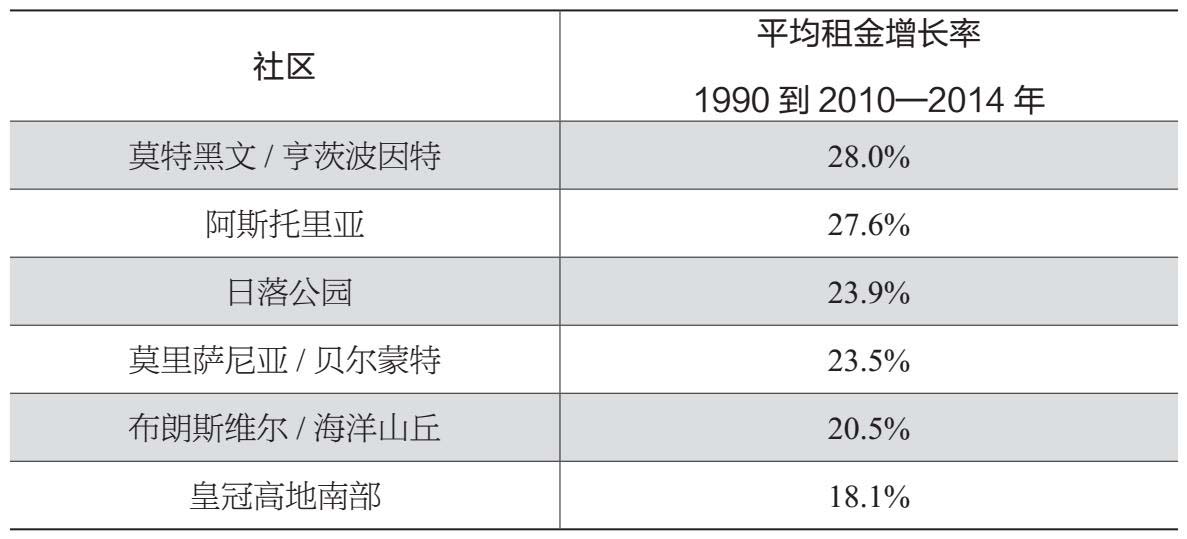
资料来源:纽约大学弗曼中心,《2015年纽约市住房和社区状况》,2016年5月。
布鲁克林的社区间房价差异更大。从“布鲁克林化”这个词就能看出来它已然是绅士化的代名词了,尽管很多人认为布鲁克林已经变成了嬉皮士和年轻白人家庭的乐园,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少数族裔的贫困社区,其中部分社区的房价甚至下跌了。2004—2014年,新潮的威廉斯堡社区的房价猛增269%;格林堡房价增长126%;尽管有污染严重、洪水频发并被列为有害物质场所的工业运河,格瓦纳斯区的房价也增长了92%;布鲁克林中心的房价增长超过70%;有同样增幅的还有历史悠久、全是维多利亚式木结构房屋的迪特马斯公园社区,以及1991年发生过暴乱的黑人和哈西德派犹太人社区皇冠高地;波恩兰姆小丘的房价增长了69%;展望莱弗茨花园社区房价增长了68%;以前是工业区的丹波和日落公园社区房价增长了61%;全是华丽联排别墅的公园坡社区房价增长了60%。 [24]
而其他一些布鲁克林社区的房价则下跌了。2004—2014年,受飓风“桑迪”影响,格里森海滩社区房价下跌了30%;地铁线路不发达的偏远中产阶级社区汉密尔顿堡房价下跌了10%;工人阶级社区卡纳西的房价下跌了12%。交通不便的低收入社区弗雷特兰斯区和雷姆森村房价则分别下跌了8%和27%。绅士化很少出现在交通不便、其他投资也很少的社区。
不论绅士化发生在哪里、影响范围有多大,它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被挤走的人。研究绅士化及其取代效用的学者兰斯·弗里曼发现,在绅士化过程中被取代和挤走的人数比人们想象中的少得多。弗里曼和他的同事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在纽约市,未绅士化社区的贫穷家庭比绅士化社区的贫穷家庭更可能离开原社区。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绅士化社区里的贫穷家庭数量更少。这项研究还指出,哪怕没有发生任何取代效应,社区的贫困居民比例也可能在10年里从30%缩小至12%。弗里曼的其他研究指出,绅士化社区弱势家庭离开原社区的可能性比未绅士化社区的弱势家庭低15%。另外,绅士化社区任何一个单独家庭被取代的可能性只有1.3%。
基于弗里曼成果的另一项研究区分了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的影响和对租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绅士化社区,租户被取代的风险比自有房住户高2.6%(和离婚率一样),但没有证据显示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有取代效应。 [25] 研究的重要结论是,绅士化的直接取代效应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重,它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绅士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真正的影响。
导致以上结论的部分原因在于,绅士化要么就发生在从前少有人住的老工业社区,要么就发生在工人阶层社区。后者的房主因绅士化带来房价上涨而获益,被取代的租客也很容易在附近社区找到条件相当的住处。绅士化很少发生在长期贫困并且社会问题重重的社区。总之,对绅士化直接取代效应的过度关注是模糊焦点的烟幕弹,这让人们忽视了再城市化和绅士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的更大伤害。
绅士化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最负面影响并不是发生在绅士化社区自身的,而是通过对房价的涓滴效应或涟漪效应,影响了绝大多数穷人生活的更贫困的社区。2015年的一项研究通过信用记录数据分析了费城从2002—2014年受到的绅士化影响,说明了涟漪效应的作用机理。 [26] 总体来看,只有15%的调查地区发生了绅士化。研究得出了和弗里曼相同的结论,即绅士化的直接取代效应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在研究期间,费城绅士化社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家庭收入提高了42%,绅士化社区弱势居民的经济状况也改善了;而未绅士化社区的家庭收入则下降了20%。另外,绅士化社区居民离开原社区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高于未绅士化社区。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绅士化社区中最贫困的底层居民确实被挤出了原来的家园,只能搬去更贫困、犯罪率更高、学区更差的社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则能跟上绅士化的脚步,甚至能从它给社区带来的改善中获益。即便是离开,他们也能利用这些收益搬到城市的体面社区,或者郊区更实惠的社区。而最贫困的底层群体则被打发到了最落后的社区,面临可能不断上涨的房租。给城市贫困人群造成最严重的打击的正是这种涟漪效应,而不是对单个住户的直接取代。
费城的例子具有指导意义,不过绅士化的涟漪效应最强的地方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它们的再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在纽约市,房租占税前收入30%以上的重租金负担家庭占比从2000年的41%上升到了2014年的52%。该比值在绅士化社区从42%上升到53%,而在未绅士化社区则上升得更多,从46%上升到近60%,再次证明了绅士化的涟漪效应。另外,底层家庭受房价冲击最大,2014年在该类人群里重租金负担家庭占比超过了75%。 [27]
在某些绅士化快速发展的城市,取代效应本身的威胁也在增强。2015年的研究显示,旧金山有超过1/4的社区面临居民被大量取代的风险。 [28] 随着对昂贵有限空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到2030年,取代规模还会大幅上升。尽管直接的取代效应在过去不是严重的问题,但随着房价不断上升,更多社区发生变化,取代效应以后可能会成为超级城市的难题。随着绅士化的发展,不仅底层群体会苦不堪言,本地老居民和后来的新居民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绅士化者和原住居民——新来的人和可能被挤出去的人,看待社区及其改变的视角截然不同。李在普瑞特艺术学院演讲时问观众:“他们现在叫布什维克什么?那个词是什么?”“东威廉斯堡。”观众回答。他咆哮道:“那帮房地产混蛋把它的名字都改了!名字怎么能改呢?” [29]
激怒李的这种文化抹杀的确真实存在。一项有关绅士化的民族志研究调查了费城南部某低收入黑人社区,揭示了老居民和新居民在绅士化进程中不同的经历。 [30] 研究者询问居民社区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他们常用的社区名字。黑人居民倾向于用社区从前的名字,如南费城。而白人居民则喜欢用新名字,如研究生医院、南里顿豪斯或西南市中心。白人居民普遍认为社区中少数族裔聚集区的犯罪率更高,实际上这些区域的犯罪率低于富裕白人更多的区域。种族决定了居民观察和描述社区变化的视角,白人和黑人居民定义社区的差异并不受收入水平或居住年限的影响。“白人居民的社区定义有很多种,但就是没有少数族裔的定义方式。”研究写道:“社会群体共同构建的大型包容性社区最终被取代了。”换句话说,老社区被新居民重新定义了。
从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热门餐厅的评论中也能看到种族和绅士化的关系。热门餐厅往往是绅士化和社区变化的象征。2015年的一项研究通过Yelp(点评网站)上的餐厅点评调查了人们对布鲁克林两个绅士化社区的大众印象,一个是传统的波兰社区绿点,另一个是传统黑人社区贝德福德-斯图文森。Yelp点评用户认为绿点代表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但对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的印象则大不相同,常用“危险”“粗糙”“贫民窟”来形容它。但是他们认为新餐厅有利于促进社区改变。某Yelp点评用户评价一家餐厅,说它“正是贝德福德-斯图文森所需要的地方”。 [31] 这类研究说明,绅士化社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集体构建和重建的,以及种族对人们感知绅士化的影响。在社区定义问题上,绅士化者总是有更大的话语权。
不幸的是,种族甚至更能决定哪些社区不会发生绅士化,并维持长期贫困。根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1995—2014年,芝加哥经济增速最快的社区都是白人社区,最慢的都是黑人社区。 [32] 该研究跟踪了99个正经历绅士化或可以绅士化的社区,其中有26个在1995年已经开始绅士化,16个处于绅士化边缘,还有57个与绅士化社区相邻,开始绅士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项研究最有趣的一点是,它利用谷歌街景跟踪新建楼盘、老建筑的维护水平和其他可见迹象,以此定位绅士化社区。该研究发现,相比居民收入、教育程度等典型因素,种族才是社区是否发生绅士化的关键因素。
总体看来,黑人居民比重越高,社区绅士化的可能性就越小。绅士化社区的白人居民占比均不低于35%,黑人居民占比则不超过40%。黑人居民超过40%的社区一般经济状况鲜有改善,倾向于持续贫困。这种种族门槛从根本上阻止了绅士化的蔓延,或者说,绅士化发生的界限分明,几乎不会向黑人社区蔓延,即便这些黑人社区与绅士化社区的距离很近。当然也不排除有例外发生,比如纽约的哈林区、皇冠高地和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等传统黑人社区也发生了绅士化。但研究传递的主要信息令人深思,即大量黑人社区几乎完全隔绝了绅士化,居民普遍陷于长期贫困。这一结论适用于绝大多数城市。
种族集中贫困构成了更严重的城市问题。一项覆盖全美51个人口数大于100万的大城市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1970年的贫困社区在30年后依然贫困。研究跟踪了这些城市市中心方圆10英里内的所有高贫困社区,发现在1970—2000年间发生绅士化的调查社区中,有10个社区一直处于贫困状态,12个从稳定状态陷入集中贫困。只有极少数贫困社区的经济状况获得了实质性改善,仅有105个调查社区(占总数的10%)的贫困率下降到15%以下,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而1200个调查社区从低贫困社区(贫困率低于15%)变成了高贫困社区(贫困率高于30%)。更令人震惊的是,高贫困社区的总数增加了两倍。 [33] 归根结底,城市的长期集中贫困问题比绅士化严重多了,这可以说是最棘手的城市难题。
绅士化作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面临的重要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它带来的痛苦确实真实存在,应当认真对待。但被绅士化完全忽略的社区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它们长期存在的种族集中贫困还在不断恶化。
与其本能地抵制城市变化,不如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抑制城市和社区投资毫无意义,尤其是某些社区还极其需要投资。城市政策不应抑制能促进市区经济复苏的市场力量,而应改善落后地区的住房、经济机会和社区状况,本书的最后一章还会回到这个话题。
从根本上说,绅士化是美国新阶层地理分布的城市表现,它在再城市化进程最快和空间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最为显著。美国的阶层分化不断深化,在不同城市有不同体现形式。在某些城市,阶层分化体现为城市内部的优势和弱势地区的分化;在其他城市,则体现为城市与郊区的分化。尽管表现形式不同,阶层分化都反映了新阶层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它们是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这也是接下来三章的主题。接下来,我将深入讨论经济不平等,它正深深融入美国的新阶层地理分布中。
[1] Joe Coscarelli, “Spike Lee’s Amazing Rant Against Gentrification: ‘We Been Here!,’” New York Magazine, February 25, 2014,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2/spike-lee-amazing-rant-against-gentrification.html. Lee’s rant set off a firestorm of reaction. See John McWhorter, “Spike Lee’s Racism Isn’t Cute: ‘M——F——Hipster’ Is the New ‘Honkey,’”TIME, February 28, 2014, http://time.com/10666/spike-lees-racism-isntcute-m-f-hipster-is-the-new-honkey; Gene Demby, “The One Problem with Spike Lee’s Gentrification Argument,” Salon, February 27, 2014, www.salon.com/2014/02/27/the_one_problem_with_spike_lees_gentrification_argument_partner.
[2] Neil Smith,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6); Neil Smith,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 no. 4 (1979); Neil Smith, “Gentrific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58, no. 2 (April 1982):139–155; Neil Smith, “Of Yuppies and Housing: Gentrification, Soc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Drea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5, no. 2 (January 1987): 151–172.
[3] Susie Cagle, “Fallacy of the Creative Class: Why Richard Florida’s ‘Urban Renaissance’ Won’t Save U.S. Cities,” Grist, February 11, 2013, http://grist.org/cities/fallacy-of-the-creative-class.
[4] Daniel Hertz, “There’s Basically No Way Not to Be a Gentrifier,” CityLab,April 23,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04/theres-basically-no-waynot-be-gentrifier/8877.
[5] Lance Freeman, “Five Myths About Gentrification,” Washington Post,June 3, 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ive-myths-aboutgentrification/2016/06/03/b6c80e56-1ba5-11e6-8c7b-6931e66333e7_story.html;Douglas Massey, “Comment on Jacob Vigdor, ‘Does Gentrification Harm the Poor?’”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2, 174–176.
[6] Ruth Glass,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1964).
[7] Tino Balio, United Artists: The Company That Changed the Film Industry(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8] Dennis Gale, “Middle Class Resettlement in Older Urban Neighborhoods:The Evidence and th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 no. 3 (1979): 293–304.
[9] Rosen, quoted in Wayne King, “Changing San Francisco Is Foreseen as a Haven for the Wealthy and Childless,”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www.nytimes.com/1981/06/09/us/changing-san-francisco-is-foreseen-as-a-havenfor-wealthy-and-childless.html.
[0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10] William Easterly, Laura Freschi, and Steven Pennings, “A Long History of a Short Block: Four Centuries of Development Surprises on a Single Stretch of New York City Street,” NYU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RI Working Paper no. 96, 2014, http://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51873de4b008f3c5898336/t/54cfbedee4b092432af5f 5f8/1422900969104/DRIw1.pdf. The project website is www.greenestreet.nyc. 也参见 Laura Bliss, “The Economic Lessons in a Single New York City Block,” CityLab, August 3, 2015, www.citylab.com/design/2015/08/theeconomics-lessons-in-a-single-new-york-city-block/400154。
[11] Yonah Freemark, “Reorienting Our Discussion of Urban Growth,” The Transport Politic, July 6, 2016, www.thetransportpolitic.com/2016/07/06/reorienting-our-discussion-of-city-growth.前一百大城市中,从2000年到2014年市中心区域(以市政厅位中心,方圆1.5英里的区域)人口增长的城市有53个。同样实现市中心人口增长的城市数量在1990年到2000年间是51个,1980年到1990年间是35个,1970年到1980年间只有6个,1960年到1970年间只有5个。
[12] Jed Kolko, “Urban Revival? Not for Most Americans,” JedKolko.com, March 30,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3/30/urban-revival-not-for-most-Americans.
[13] Markus Moos, “From Gentrification to Youthificatio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Young Age in Delineating High-Density Living,” Urban Studies 53, no. 14 (November 2016): 2903–2920, http://usj.sagepub.com/content/53/14/2903.long.
[14] Terra McKinnish, Randall Walsh, and T. Kirk White, “Who Gentrifies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 no. 2 (2010):180–193. 这项研究也指出,绅士化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群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没有读完高中的黑人家庭是最容易被挤出绅士化社区的群体,而留下来的黑人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群体。
[15] Nathaniel Baum-Snow and Daniel Hartley, “Accounting for Central Neighborhood Change, 1980–2010,”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September 2016, www.chicagofed.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6/wp2016-09.
[16] Miriam Zuk, Ariel Bierbaum, Karen Chapple, Karolina Gorska, 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Paul Ong, and Trevor Thomas,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and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2015, www.frbsf.org/communitydevelopment/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5/august/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role-of-public-investment/.
[17] Sam Bass Warner J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 Lena Edlund, Cecilia Machado, and Michaela Sviatchi, “Bright Minds, Big Ren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ising Returns to Skill,”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72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ember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729.也可参见Victor Couture and Jessie Handbury, “Urban Revival in America, 2000 to 2010,”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5,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couture/download/Couture_Handbury_Revival.pdf。
[19] Daniel Hartley, Gentrification and Financial Heal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2013, www.clevelandfed.org/newsroom-and-events/publications/economic-trends/2013-economic-trends/et-20131106-gentrification-and-financial-health.aspx.
[20] 绅士化与以下因素正相关:人口规模(0.59)和人口密度(0.44);人均收入(0.61)和工资(0.62);某城市地区中科学与技术工人的占比(0.32);高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0.58);创意阶层劳动力占比(0.55);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1)。绅士化与以下因素负相关:某区域内蓝领工人占比(-0.48)。它还与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人数占比(0.61)正相关,与独自驾车上下班的人数占比(-0.55)负相关。详见附录的表2。
[21] James Tankersley, “Why the PR Industry Is Sucking Up Pulitzer Winners,”Washington Post, Wonkblog, April 24, 2015,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5/04/23/why-the-pr-industry-is-sucking-up-pulitzerwinners.
[22] Michael Bart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egy Used to Identify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December 3, 2014; Richard Florida,“No One’s Very Good at Correctly Identifying Gentrification,” CityLab,December 15,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12/no-ones-very-goodat-correctly-identifying-gentrification/383724.
[23] NYU Furman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Urban Policy,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May 2016, http://furmancenter.org/files/sotc/NYUFurmanCenter_SOCin2015_9JUNE2016.pdf.
[24] 数据来自 PropertyShark.com。
[25] Lance Freeman, “Displacement or Succession?,” Urban Affairs Review 40,no. 4 (2005): 463–491; Lance Freeman and Frank Braconi,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New York Cit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0, no. 1 (2004): 39–52; Lance Freeman,“Neighborhood Diversity, Metropolitan Segregation, and Gentrification:What Are the Links in the US?,” Urban Studies 46, no. 10 (2009): 2079–2101.关于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和租房者的影响,参见On the effects of gentrification on homeowners and renters, see Isaac William Martin and Kevin Beck, “Gentrification, Property Tax Limitation, and Displacement,”Urban Affairs Review, September 2, 2016, http://uar.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6/08/31/1078087416666959.abstract. 也参见 Kathe Newman, “The Right to Stay Put, Revisited: 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Displacement in New York City,” Urban Studies 43, no. 1 (2006): 23–57; Ingrid Gould Ellen and Katherine M. O’Regan, “How Low Income Neighborhoods Change: Entry, Exit, and Enhance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1, no. 2 (2011): 89–97。
[26] Lei Ding, Jackelyn Hwang, and Eileen Divringi, “Gentr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Philadelphi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October 2015.
[27] Furman Center,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http://furmancenter.org/research/sonychan.
[28] Miriam Zuk, Regional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Displacement, Centre for Community Innovation, 2015, www.urban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rews_final_report_07_23_15.pdf.
[29] Coscarelli, “Spike Lee’s Amazing Rant Against Gentrification.”
[30] Jackelyn Hwa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 Reifying and Redefining Identity and Boundaries in Inequal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52, no. 1 (January 2016): 98–128.
[31] Sharon Zukin, Scarlett Lindeman, and Laurie Hurson, “The Omnivore’s Neighborhood? Online Restaurant Reviews, Race, and Gentrific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October 2015).
[32] Jackelyn Hwang and Robert J. Sampson, “Divergent Pathways of Gentrification: Racial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enewal in Chicago Neighborhoo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no. 4 (August 2014):726–751.
[33] Joseph Cortright and Dillon Mahmoudi, Neighborhood Change, 1970 to 2010: Transition and Growth in Urban High Poverty Neighborhoods,Impresa Economics, May 2014, http://dillonm.io/articles/Cortright_Mahmoudi_2014_Neighborhood-Change.pdf.
2012年前,出了布鲁克林或者纽约的政治圈就几乎没人知道谁是比尔·白思豪了。2009年他当选为代表全市的纽约市公共议政员,而此前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里,他都在市议会里代表布鲁克林的第39区,包括较高端的社区科布尔山和公园坡、卡罗尔花园、格瓦纳斯和温莎台等新绅士化社区,以及肯辛顿和市政公园等蓝领社区。2013年,媒体巨头创始人、传奇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结束了他的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纽约市长任期,白思豪决定竞选市长。但人们认为他胜算不大,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市议会代言人和布隆伯格的同僚克里斯蒂娜·奎因会当选下一任市长。 [1]
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纽约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强势复苏。 [2] 创意产业、科技产业及金融、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传统经济支柱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就业率在2011年就重回危机前的高峰值。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失去3万多个就业岗位的金融业也逐渐恢复生机,银行家和分析师又能拿到高额薪金了。建设工程在曼哈顿下城的世贸大厦遗址、切尔西北的哈德逊广场、威廉斯堡的东河沿线、布鲁克林市中心等地大规模展开。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几乎消失殆尽的科技行业也恢复了生机,布隆伯格政府还发起投入20亿美元在罗斯福岛为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一座占地200万平方英尺的应用科学工程校区。
街道空前整洁,充满活力,暴力犯罪大大减少,游客数量达到纪录高位。由于新建了自行车道和共享单车设施,曼哈顿街头还出现了很多单车。不论是资本还是人才,纽约都走在世界前列,而这两者正是城市成功的关键。布隆伯格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城市如果想吸引创造性人才,就一定要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他还借鉴了我的创意经济观点,补充道,“经济学家可能不会这样说,但事实就是:酷很重要。当人们发现一个有优质公园、安全的街道且交通方便的社区能给他们提供灵感时,他们就会用脚投票”。 [3]
布隆伯格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市长之一,本来他在任职的最后几年只需庆祝胜利就行了,但还是出了些问题。尽管纽约从2002年开始就重新繁荣起来,但大量纽约人却完全没有富足的感觉。大家公认纽约的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则越落越远。到2013年,曼哈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总收入的88倍。纽约的百万富翁人数约40万,超过了新奥尔良、匹兹堡、克利夫兰或明尼阿波利斯的全市人口。然而,实际工资下降和房价飙升让大多数纽约人的生活质量下滑了。2013年8月,《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发现,55%的选民认为布隆伯格的政策对富人更有利,当被问到纽约是否已经“太贵而无法生活”时,85%的人选了“是”。 [4]
受到民粹主义者抵制城市经济分化扩大的浪潮推动,白思豪围绕不平等展开自己的竞选活动。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他强调纽约已经变成了“双城记”。他在2013年春天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做出改变,不采取解决不平等问题、重建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后代会发现纽约只是富人的游乐场,在这个镀金城市里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能成功,而成百上千万的纽约人每天都要艰难地维持生计。”“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经济也没有任何城市能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繁荣。” [5] 为了改变这一趋势,他承诺给富人增税,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拓展课后活动项目,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低薪行业的就业岗位,建造成千上万的经济适用房。
然而学者和政治预言家都没想到,2009年9月白思豪轻松淘汰了克里斯蒂娜·奎因和比尔·汤普森,一举赢得党内初选,比尔在2009年市长竞选中还曾差点击败布隆伯格。白思豪的共和党对手、前大都会运输署主席乔·勒霍塔说,白思豪是顽固不化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政策会摧毁城市经济。但选民并没有买乔的账,白思豪赢得了73%的大众选票,在部分人群中占比甚至更高——95%的黑人选票、87%的拉丁裔选票和86%的年薪低于5万美元人群的选票。 [6]
白思豪的竞选活动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基本事实:城市不平等在不断加深,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城市问题,长期来看,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发展。尽管成因和推动力可能不同,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几乎是所有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综合各种衡量方式来看,它在发达城市最严重。城市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知识和科技的密集程度越高,就越不平等。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也不只有不平等,它们的成功还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人才和企业聚集密不可分。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不平等急剧加深,在经历了罗斯福新政到里根当选期间的温和发展后,收入不平等迅速攀升到20世纪20年代盖茨比时代的水平。从1928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到1979年里根总统当选,除了阿拉斯加之外,所有州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的收入在州总收入中的占比都在下降。而在2007年,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占有全国23.5%的收入,达到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1979—2007年,超过一半的全国收入增长(53.5%)都进了前1%人群的口袋;2008年经济危机后,这一比值达到惊人的85%。2013年,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的人群收入的25倍。 [7]
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和先进科技中心,前1%人群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甚至更大。在纽约,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人群的40倍;在洛杉矶、旧金山和圣何塞,这一比值达到30倍。 [8]
美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很高,基尼系数达到0.450(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不平等程度最高),与伊朗相当,比俄罗斯、印度或尼加拉瓜还高。美国很多城市的基尼系数更高,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相当——纽约的基尼系数接近南非的斯威士兰,洛杉矶接近斯里兰卡,波士顿接近萨尔瓦多,旧金山接近卢旺达,而迈阿密则接近津巴布韦。当然,纽约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至于像斯威士兰的穷人那么糟,但美国城市的贫富差距确实和世界上最贫困、最不平等的地方差不多。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十分可悲,令人忧心(见表5.1)。 [9]
表5.1 美国城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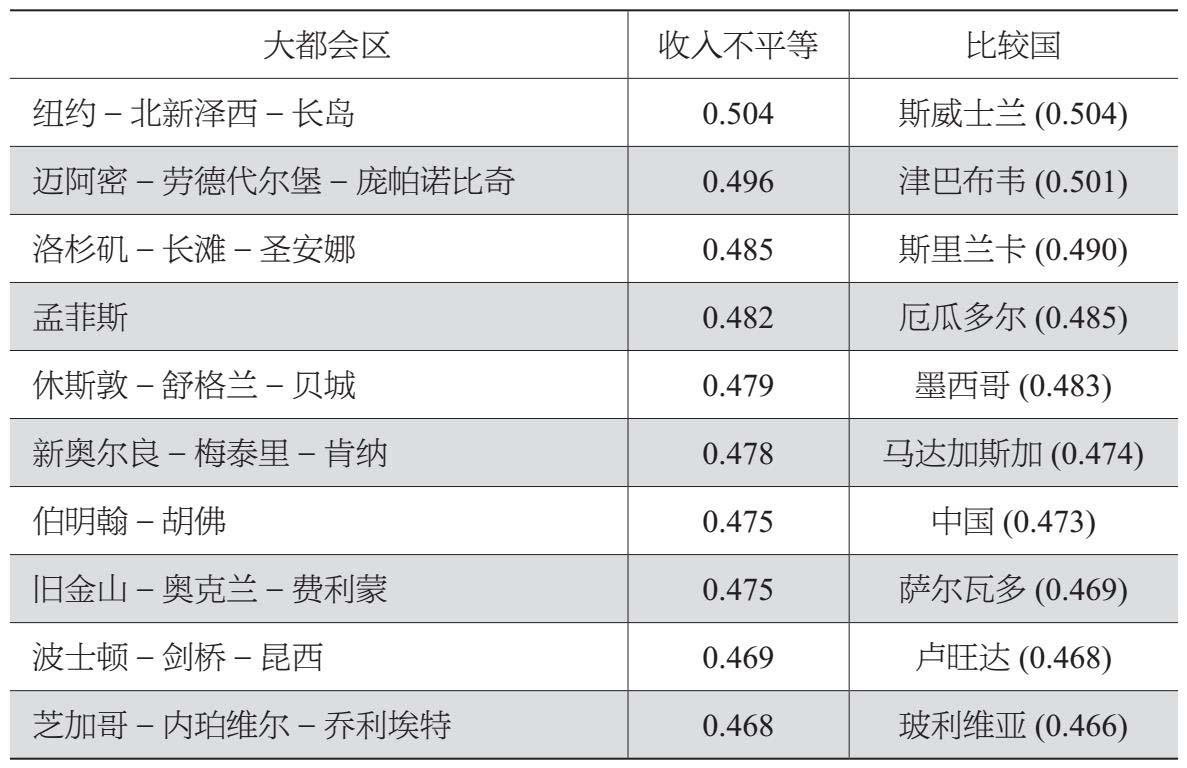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城市和国家中情局人口普查所取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
美国城市的不平等程度在迅速攀升。2006—2012年,美国有2/3的城市(356个城市中的226个)不平等程度变高了,并且核心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都会区。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本身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它们所在的大都会区,甚至高于波士顿和迈阿密的中心城区,华盛顿、亚特兰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高于各自的都会区。 [10]
收入不平等在有的地方是富人收入上升的结果,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由穷人收入下降造成的,在“95-20比”为10~18的高比值城市就可见一斑。“95-20比”是指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与最低的20%家庭的年收入之比。 [11] 如表5.2所示,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平均收入超过了550000美元。同样由前5%的家庭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城市还有纽约和洛杉矶这种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这种知识中心。但在有的高“95-20比”城市,低收入群体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比如高度依赖服务经济并存在种族集中贫困的“太阳地带”城市新奥尔良和迈阿密。
表5.2 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续表

资料来源:艾伦·贝鲁布和娜塔莉·霍姆斯,《因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城市不平等》,布鲁克林研究所,城市政策规划,2016年1月14日。
与收入不平等不同,工资不平等是另一个衡量美国城市经济分化问题的视角(见表5.3)。收入不平等的计算中既包含租金和资本收入,也包含底层无业群体的经济状况,而工资不平等只衡量了工资最高和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由于技术人员和知识工作者的工资很高,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尤其高。全美工资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方是位于硅谷中心的圣何塞。排名前十的城市和地区还有纽约、洛杉矶、奥斯汀科技中心、圣迭戈、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华盛顿、旧金山、达拉斯和亚特兰大。
表5.3 工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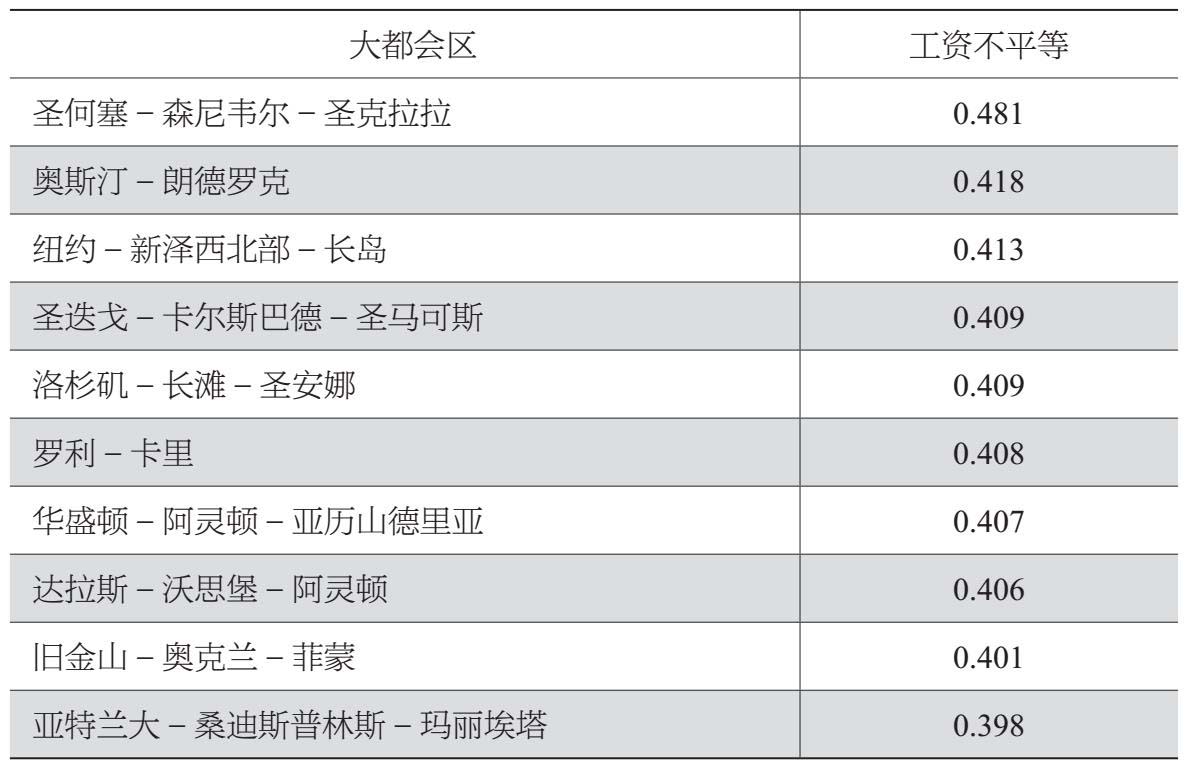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工资不平等数据。
和收入不平等一样,可以通过比较工资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的工资差距来观察工资不平等的极值,即“9010比”(见表5.4)。全美工资最高的前10%人群工资约为最低的10%人群工资的5倍。 [12] 但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差距更大,圣何塞的90-10比超过7倍,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的比值约为6倍,洛杉矶和波士顿的比值约为5.5倍。
表5.4 工资差距最大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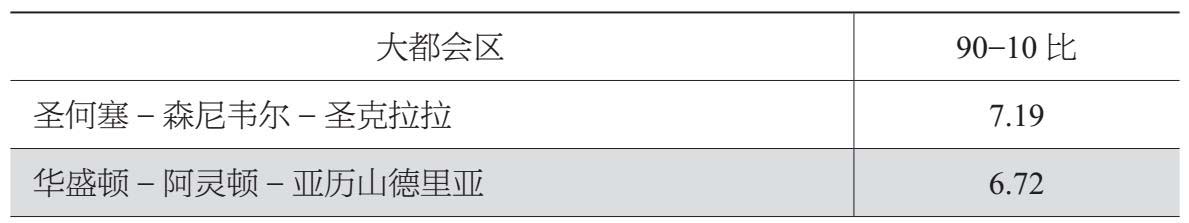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从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可以看出,美国城市地区的经济不平等有不同的特征和起因。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现这两种不平等源自两种不同的现象,因此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城市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几个共同影响因素:(1)全球化与技术变革;(2)种族和集中贫困的长期影响;(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社会契约的削弱。 [13]
工资不平等主要是由那些提高高收入群体工资的因素导致的,比如经济家所说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14] 全球化让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入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技术革新和生产率上升又淘汰了更多这类工作岗位。曾是中产阶层的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劳动力慢慢分化为两极,少数是高薪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而多数是低薪的日常服务业从业者。我们发现工资不平等与大学生、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和高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有统计相关性 [15] ,所以工资不平等在前沿知识中心尤其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收入不平等则更能反映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长期贫困和经济困境。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等社会学家认为,不平等是贫穷和种族弱势的产物 [16]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及用黑人人口占比衡量的种族均具有统计相关性。 [17] 另外,工会成员占比越高,收入不平等越低;税率越低,收入不平等越高。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工会力量削弱和用来支持社会保险的累进税率的降低具有统计相关性。
换句话说,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共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它不只是全球化和自动化等结构性经济变革的结果,也源于那些破坏旧社会契约和侵蚀美国工人工资的公共政策,如减税、缩减福利和反工会措施等 [18] ,而这些政策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的。
不论根源是什么,不平等问题在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最为严重。 [19] 为了全面了解城市的不平等状况,我把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合并为一个“综合不平等指数”(见图5.1和表5.5)。根据这一指数,美国最不平等的前三个大城市地区是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第四是休斯敦,第五是夏洛特,随后是费城、达拉斯、波士顿、芝加哥和伯明翰。总之,美国所有前五大城市和前十大城市里的七个都在前十大最不平等大城市地区的名单中。如果考虑所有城市地区,美国最不平等的地方则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另外,由于高薪的教职员工与低薪的服务人员和在职学生存在巨大工资差异,大学城往往也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城市地区 [20] ,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大学城(得州农工大学)、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杜克大学)、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泰特科利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密歇根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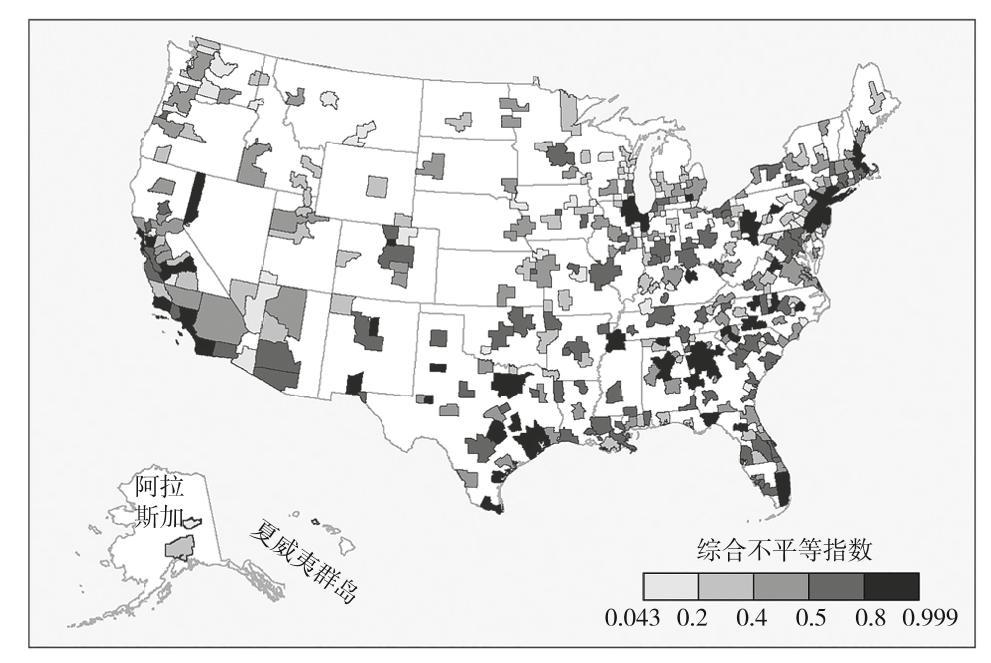
图5.1 综合不平等指数(1)
表5.5 综合不平等指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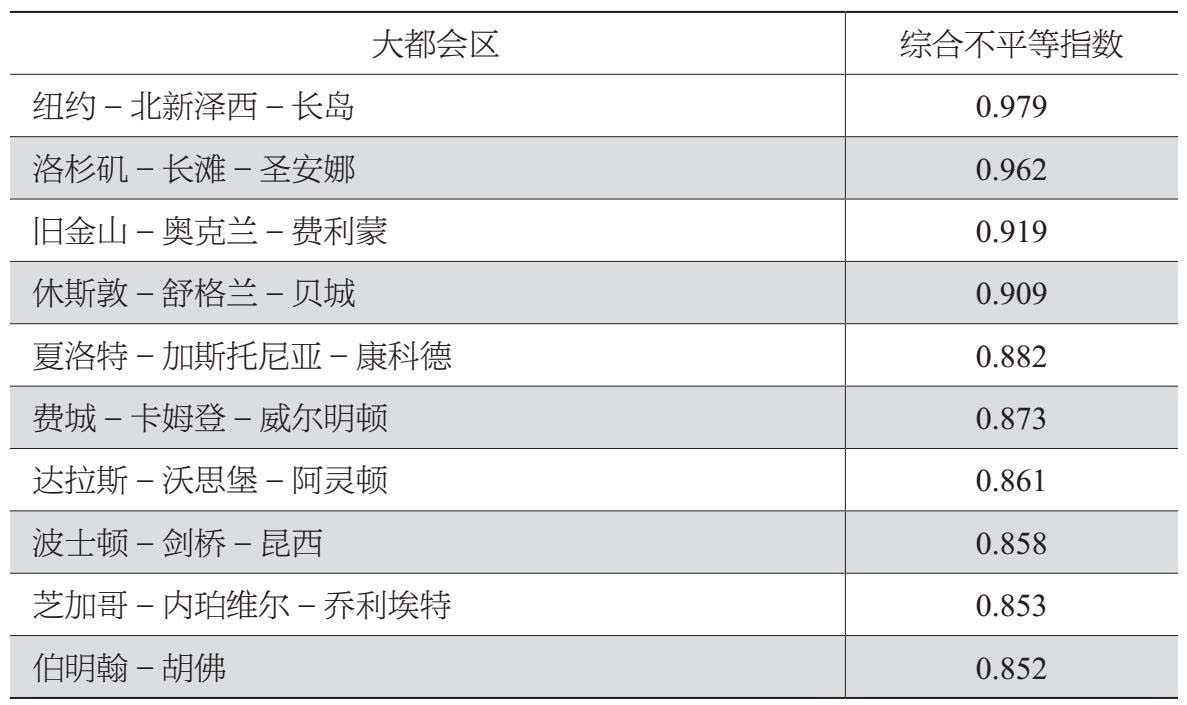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的不平等数据。
注:该项指数结合了收入和工资不平等。
但是,如果大学城只是反映了劳动力的经济不平等,那么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中心还在创造这种不平等。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行业越聚集,经济不平等就越突出。 [21] 这又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症结:正是那些驱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制造了不平等。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有近70%城市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异(以“90-10比”衡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达到50万~100万的城市中,只有34%的工资差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比值在人口为10万~50万的城市中仅为10%,在人口10万以下的城市中则低于3%。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纳撒尼尔·鲍姆-斯诺进行的两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一关系。其中一项表明,从1979—2004年,剔除教育、技能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影响后,25%~35%的经济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从1979—2007年,1/3的工资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 [22]
由于大城市的政治倾向最偏自由派,所以最自由派的城市也是最不平等的城市。这使得大城市的民主党市长(如比尔·白思豪)把减少不平等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核心显得颇为讽刺。然而整体来看,美国政治倾向偏自由派的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保守派地区。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25个国会选区都是由民主党议员代表的。 [23] 而我自己在对350多个美国城市地区的研究中也发现,工资不平等程度与自由派政治倾向正相关,与保守派政治倾向负相关。 [24] 不平等当然不是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直接产物,而是与自由派一样,都是人口密集的知识型大城市的特征之一。另外,越来越多的富裕高学历人群在搬回城市,他们也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
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不公平,还会阻碍经济发展。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控制教育、技术水平和其他促进城市发展的变量后,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25] 根据2014年的另一项研究,城市的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期越短。研究分析了1990—2011年期间约200个城市地区,发现在就业增长期较短的城市中,不平等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就业增长期越短;不平等程度越低,就业增长期越长。更准确地说,收入不平等每增加1%,就业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上升20%。 [26]
此外,美国几乎没有城市能同时实现高经济增长和低不平等,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来自2016年的两项研究。第一项研究从两个维度分析了美国前100个大城市,一个维度是社区的不平等程度(按照邮政编码划分),另一个维度是繁荣或贫穷程度(通过收入中位数、就业增长、教育水平、新店开张情况等因素衡量),结果发现只有9个城市同时实现了高度繁荣和高度平等。这些城市普遍面积不大,并向郊区散漫扩张,比如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普莱诺、得克萨斯,或麦迪逊、威斯康星等较富裕和人们的起步收入较同质化的大学城。如图5.2所示,旧金山和圣何塞这样的前沿科技中心高度繁荣且高度不平等,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和波士顿也相对繁荣且高度不平等。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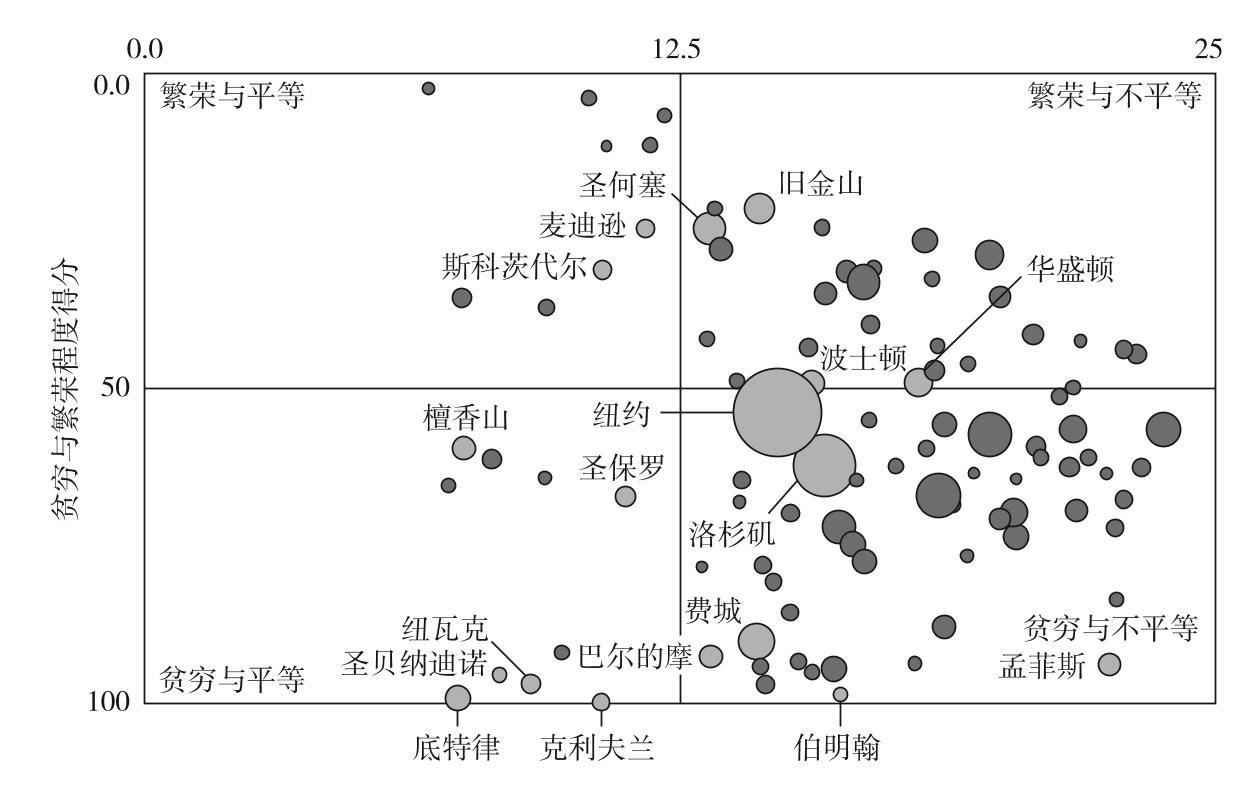
图5.2 不平等与繁荣之间的脱节
资料来源:《2016年贫困社区指数》(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经济创新集团,2016年。
注:圆圈大小反映人口总量。
第二项研究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它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一个衡量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社会贫困程度和种族分化的指标)之间的联系。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低薪群体和穷人的经济状况。 [28] 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指标,研究对象也变成了城市而非城市地区,但这项研究也发现从2009—2014年,美国100个大城市中仍然只有9个城市的社会包容性提高了,尽管有95个都经历了经济增长。
如果高度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那么高度平等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美国城市里很难看出这一规律,因为美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太高。如果观察不同国家的不平等与先进创意经济的关系,这一规律就很明显了。这些国家中有很多不平等程度都低于美国,还有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远比美国发达。我们通过对比139个国家的不平等与创意经济实力(基于全球创造力指数,这是一个衡量各国技术实力、人才水平和包容度的综合指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经济体越创新,不平等程度越低。图5.3展示了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和创造力水平,向下倾斜的直线表明两者基本呈负相关关系。 [29]
第二,如果考察不平等与创意经济的竞争力的关系,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上方,包括美国和英国,它们的创新实力很强,也高度不平等。第二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下方,包括瑞典、芬兰和丹麦,它们的创新水平也很高,但不平等程度大大降低。它们代表了国家最大化创新实力的两种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收入高度不平等的“低路”路径,以及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收入较平等的“高路”路径。只有后者才能在不产生负面影响(严重不平等和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产生正面效用(高水平的创新实力、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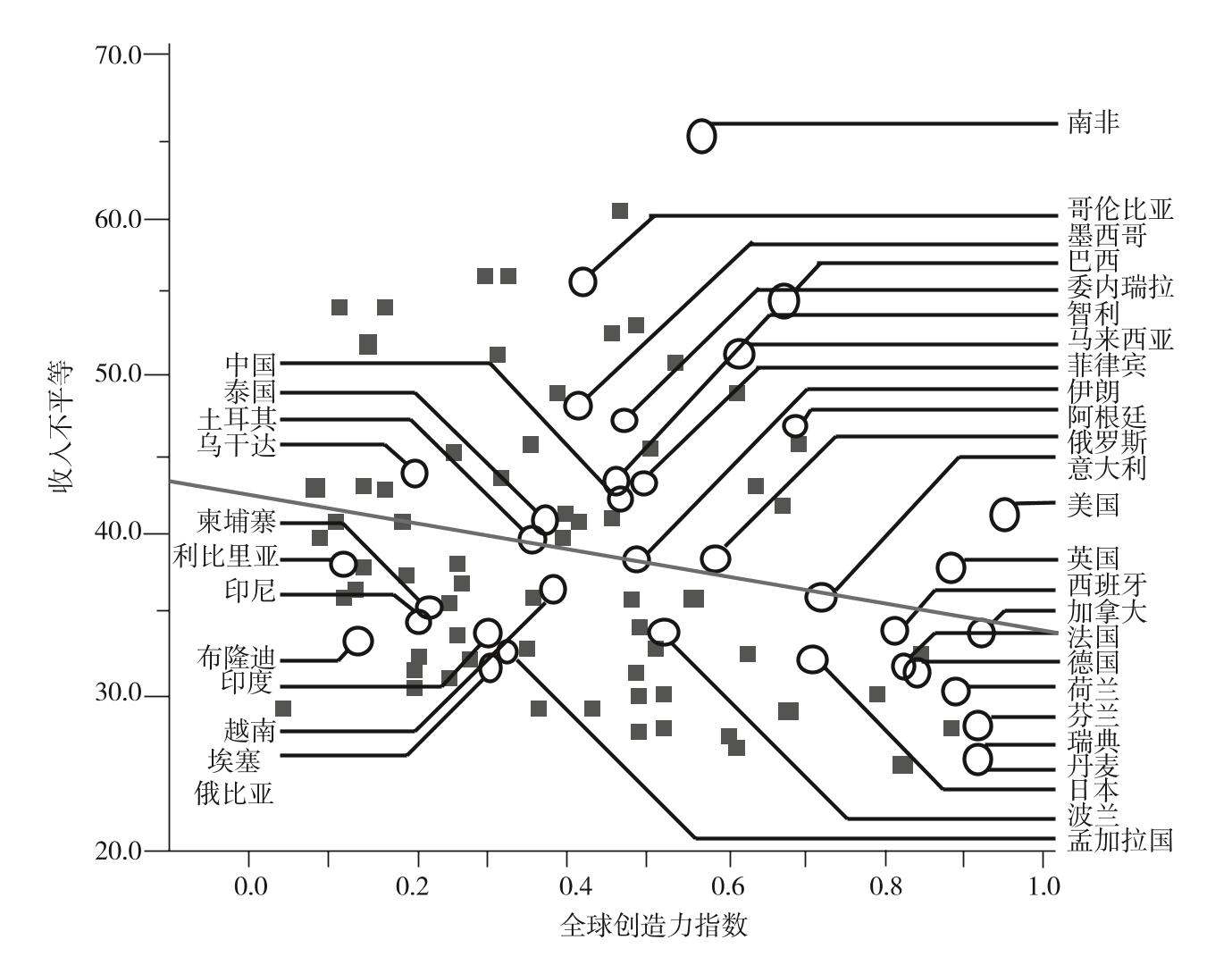
图5.3 不平等与全球创造力
资料来源: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凯伦·金,《2015年全球创造力指数》(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 ),马丁繁荣研究所。
经济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则会促进经济发展,如累进税制和北欧发达的福利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国家不平等程度、发展水平和再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对更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平等;第二,再分配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第三,降低不平等的政策能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30] 总之,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便低不平等是由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带来的。
不平等不是城市经济的偶然失误,而是城市经济的根本特征。它的产生因素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正如聚集和发展相伴相生,聚集和不平等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平等是一个讽刺而麻烦的城市成功特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对经济增长来说聚集十分必要,但不平等却并不必要。降低不平等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它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注定不变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它们可以选择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让社会底层人群无法得到社会安全网的保障,也可以选择通过再分配和其他政策机制降低不平等,这样不仅不会牺牲发展,往往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进一步讨论城市如何兼顾发展和平等,并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繁荣。然而,城市聚集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日益严峻的经济分化或空间不平等——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被分隔在城市与郊区中完全相互独立的区域。这种经济分类的趋势比不平等问题本身更麻烦,因为它让顶层不断累积优势,而弱势群体的不利境况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严重。
[1] Sam Roberts, “Mayor Making It No Secret: He’ll Endorse Quinn in 2013,”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11, www.nytimes.com/2011/08/29/nyregion/in-private-bloomberg-backs-christine-quinn-as-successor.html.
[2]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Steven Pedigo, and Rosemary Scanlon,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August 2015, 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3] Michael Bloomberg, “Cities Must Be Cool, Creative, and in Control,”Financial Times, March 27, 2012, www.ft.com/cms/s/0/c09235b6-72ac11e1-ae73-00144feab49a.html#axzz3nuBbmXVR.
[4] Michael Barbaro and Megan Thee-Brenan, “Poll Shows New Yorkers Are Deeply Conflicted over Bloomberg’s Leg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2013, www.nytimes.com/2013/08/18/nyregion/what-new-yorkers-think-ofmayor-bloomberg.html; Sam Roberts, “Gap Between Manhattan’s Rich and Poor Is Greatest in US, Census Fi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4,www.nytimes.com/2014/09/18/nyregion/gap-between-manhattans-rich-andpoor-is-greatest-in-us-census-finds.html; “Cities and Their Millionaires,” The Economist, May 9, 2013, 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3/05/daily-chart-7; Aoife Moriarty, “Revealed: Global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Millionaires,” Spears, July 22, 2014, www.spearswms.com/revealed-global-cities-with-the-highest-percentage-of-millionaires.
[5]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 Bill de Blasio” (video),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ilano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nagement, and Urban Policy, May 30, 2013, http://new.livestream.com/TheNewSchool/Bill-de-Blasio; Bill de Blasio, “A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New York Public Advocate Archives, May 30, 2013, http://archive.advocate.nyc.gov/jobs/speech.
[6] 投票数据来自《纽约时报》的票站调查,www.nytimes.com/projects/elections/2013/general/nyc-mayor/exit-polls.html。
[7]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
[8] 在一些面积更小但超级富裕的地区,前1%和剩余99%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大,这里生活的顶级名人附近就住着低收入服务业工人和穷人。例如,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市,前1%的人收入是其他人的200倍。另外还有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73倍)、维罗海滩(63倍)、基韦斯特(59倍)、迈阿密(45倍),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74倍)、拉斯维加斯(41倍)。城市地区和更近期的国家趋势数据来自Estelle Sommeiller, Mark Price, and Ellis Wazet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6), www.epi.org/publication/income-inequality-in-theus/#epi-toc-8。
[9] 国家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The World Factbook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5),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for metros it i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
[10] 关于大都会地区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参见Richard Florida, “Where the Great Recession Made Inequality Worse,” CityLab, August 4, 2014,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4/08/where-the-great-recession-made-inequalityworse/375480/T; US Conference of Mayors, U.S. Metro Economies: Income and Wage Gaps Across the U.S., Prepared by IHS Global Insight, 2014, http://usmayors.org/metroeconomies/2014/08/report.pdf. 关于城市与大都会地区的不平等问题对比,参见Daniel Hertz, “Why Are Metropolitan Areas More Equal Than Their Central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September 22, 2015, http:// cityobservatory.org/why-are-metropolitan-areas-more-equal-than-their-centralcities; Joe Cortright,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Inequality Measurements to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July 30,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the-difficultyof-applying-inequality-measurements-to-cities。
[11] Alan Berube and Natalie Holmes, “City and Metropolitan Inequality on the Rise, Driven by Declining Incom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January 14,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6/01/14-income-inequality-cities-update-berube-holmes.
[12] J. Chris Cunningham, “Measuring Wag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US Metropolitan Areas, 2003–2013,” 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ember 2015,www.bls.gov/opub/mlr/2015/article/measuring-wage-inequality-within-andacross-metropolitan-areas-2003-13.htm; Richard Florida, “Wage Inequality and America’s Most Successful Cities,” CityLab, October 7,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10/how-wage-inequality-is-playing-out-americasmost-successful-cities/409231.
[13]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2014, 1–14;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of American Cities,” CityLab, March 5,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inequality-american-cities/861;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Puzzle in U.S. Cities,” CityLab, March 7,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inequality-puzzle-us-cities/858.
[14] 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584; David Autor and David Dorn,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5 (2013): 1553–1597;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Alan B. Krueger, “Computing Inequality: 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 (1998): 1169–1213; David H.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4 (2003): 1279–1333.
[15] 工资不平等与以下因素呈显著正相关:高科技行业聚集程度(0.74),从事知识、专业和创意职业的劳动力占比(0.68),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61)。
[16]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17]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相关度为0.5,收入不平等和种族的相关度为0.3。
[18] See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88). Also see Dierk Herzer, “Un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March 3, 2016).
[19] Richard Florida,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Cities,” CityLab,January 20,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1/inequality-and-thegrowth-of-cities/384571; Richard Florid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cessful Cities and Inequality,” CityLab, January 6,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1/the-connection-between-successful-cities-andinequality/384243.
[20] 本·卡斯尔曼提出,学生的低收入是导致大学城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参见他的文章“Inequality in College Towns,” FiveThirtyEight, April 28,2014,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inequality-in-college-towns。
[21] 工资不平等与大都市地区的规模(0.48)和密度(0.38)均呈显著正相关。
[22] Nathaniel Baum-Snow and Ronni Pavan, “Understanding the City Size Wage Gap,”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no. 1 (2012): 88–127; Nathaniel Baum-Snow, Matthew Freedman, and Ronni Pavan, “Why Has Urban Inequality Increased?,” Working Paper, Brown University, June 2014, http://restud.oxfordjournals.org/content/79/1/88.full.pdf+html.
[23] Michael Zuckerman, “The Polarized Partisan Geography of Inequality,”The Atlantic, April 7, 2014,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4/the-polarized-partisan-geography-of-inequality/360130; Joshua Green and Eric Chemi, “Income Inequality Is Higher in Democratic Districts Than Republican One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y 12, 2014,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12/income-inequality-is-higher-indemocratic-districts-than-republican-ones.
[24] 工资不平等和(用希拉里的选票占比衡量的)自由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工资不平等和(用特朗普选票占比衡量的)保守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参见Richard Florida, “Why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Inequality:Liberal Metros Face the Worst of It,” CityLab, June 4, 2014,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4/06/why-democrats-are-focused-on-inequality-liberal-metros-facethe-worst-of-it/371827。
[25] Edward Glaeser, Mathew Resseger, and Kristina Tobio, “Urban Inequalit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9, no. 4 (October 2009): 617–646.
[26] Chris Benner and Manuel Pastor, “Brother, Can You Spare Some Time?Sustain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merica’s Metropolitan Regions,” Urban Studies 52, no. 7 (2015): 1339–1356; also, Tanvi Misra,“Another Reason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in U.S. Metros: Job Growth,”CityLab, March 31,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3/anotherreason-to-promote-social-equity-in-us-metros-job-growth/389033.
[27] 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Washington, DC: 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2016), http://eig.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2016Distressed-Communities-Index-Report.pdf.
[28] Richard Shearer, John Ng, Alan Berube, and Alec Friedhoff, “Growth,Prosperity, and Inclusion in the 100 Largest U.S. Metro Areas,” Brookings Metro Monitor 2016,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January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1/metromonitor#V0G10420.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aren King, 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global-creativity-index-2015/; Richard Florida, “Greater Competitiveness Does Not Have to Mean Greater Inequality,” CityLab,October 11, 2011, www.citylab.com/work/2011/10/greater-competitivenessdoes-not-greater-inequality/230.
[30] Jonathan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Redistribution,Inequality, and Growt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4),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2015年4月,在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性在被警方拘留几天后死亡,巴尔的摩市陷入暴乱。这件事不由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的家乡纽瓦克的一起类似事件,当时引发暴乱的导火索是,传说警察杀死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但是纽瓦克在1967年暴乱发生前已经出现了经济滑坡,而巴尔的摩在暴乱发生时,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巴尔的摩的内港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和会议场所,联邦山等复兴社区正吸引富人和高学历群体重返城市,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动了巴尔的摩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事实上,大巴尔的摩地区通过发展创意经济已经跻身美国大城市地区的前二十强。
然而,虽然巴尔的摩的绅士化社区在复兴发展,但大部分其他地区都非常贫困。弗雷迪·格雷出生的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就坐落在一个可以俯瞰内港的山顶上。社区里很多排屋都是复合板房子,密不透风,没有街角商店,人行道边上的绿化带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超过1/3的社区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枪击案和谋杀案发生率是巴尔的摩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巴尔的摩的这两项指标本来就位于全国前列。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巴尔的摩市整体居民平均寿命短六年半。 [1] 弗雷迪·格雷的死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都表明,巴尔的摩已经分化为两个城市——一个是繁荣发展,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工人的城市;而另一个则是在不断沦陷,有大量陷入长期贫困的黑人的城市。
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巴尔的摩。尽管返城浪潮带来了经济发展,但美国城市地区的集中城市贫困问题却更严重了,相关数据十分惊人:2014年,有1400万美国人住在极度贫困的社区,生活在集中贫困中,这一破历史纪录的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在2005—2014年,美国100个大都会地区中有2/3都经历了集中贫困的增长。 [2] 黑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社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这一趋势所反映的问题比经济不平等更隐秘也更严重,即美国的收入、教育和阶层隔离。大约10年前记者比尔·毕晓普就注意到,美国人的隔离已经不仅限于政治信仰和文化倾向了,还出现在社会经济阶层方面,他称这一现象为“大分层”。 [3]
大分层现象到如今变得更严重了,因为现在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空间隔离加深了。在1980—2010年,全国前30的城市地区中的27个出现了富人与穷人收入隔离的上升。2009年,超过85%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在经济隔离比1970年更严重的地区。1970—2012年这40多年中,住在全富人或全穷人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5%上升到34%。 [4] 在如今的美国,经济不平等也是空间不平等: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
大分层加剧问题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从前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稳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度是美国梦的代表,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970年的近2/3(65%)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一半(40%)。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整理的数据,从2000—2014年,美国229个城市地区中有203个都经历了中产阶级人口收缩。中产阶级群体最小的城市都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华盛顿、波士顿、休斯敦、迈阿密、新奥尔良、萨克拉门托和哈特福德。根据我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的分析,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小的城市人口更密集,更可能是知识密集型城市,也更多元化,这些都是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大的城市白人更多、工人阶层更大、政治倾向更保守,这些都是经济衰败地区的特征。 [5] 并且,那些在2000年中产阶级群体较大的城市,在到2014年的十几年里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收缩。不幸的是,在经济活力最强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少,在经济滑坡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多。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分层加剧现象的广度和深度,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明了一些用于衡量收入、教育和职业经济隔离的指标。我们基于全美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通过不同群体或阶级的居住地研究他们的地理隔离。我们还创建了几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程度的指数,以及综合衡量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水平的指数。 [6]
虽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经济隔离特征,但我们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不论是基于收入、教育或职业的隔离指数,还是综合了以上几个因素整体效应的综合指数,都能发现经济隔离更加严重的地方是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以及科技行业、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更聚集的大城市。另外我们还会看到,日趋深化的经济隔离的背后驱动力是优势群体的聚集,尤其是富人的聚集,富人能利用资源把自己圈在专享社区中。
首先是收入隔离,它是受到最广泛认可和研究的经济隔离形式。我们对收入隔离的研究考虑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家庭)的地理隔离。 [7]
这里的规律和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不平等的地理分布不同。整体收入隔离程度最高的十大城市包括“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布法罗,以及孟菲斯、费城、菲尼克斯、堪萨斯和纳什维尔(见表6.1)。纽约刚好跌落前十榜单,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收入隔离程度较低。这就是说,我们更广泛的统计研究表明,收入隔离水平和城市的规模大小、人口密度以及高新科技与创意阶层的聚集程度密切相关。 [8]
表6.1 收入隔离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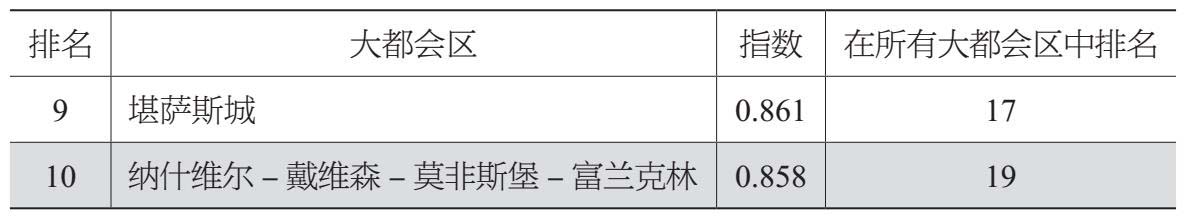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约15%的美国人——也就是4500万人口的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他们的隔离正在扩大。隔离问题领域最顶尖的两位专家——肯德拉·比肖夫和肖恩·里尔登的研究表明,住在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从1970年的8%上升到2009年的18%。 [9] 和收入隔离一样,贫困隔离最严重的地方是“铁锈地带”的密尔沃基、克利夫兰、底特律和跨越纽约和波士顿的东北走廊沿线的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以及东南部的华盛顿和孟菲斯、西南部的丹佛(见表6.2)。但是纽约排名第六,科技中心的贫穷隔离水平也高于它们的收入隔离水平。在这里,我们的统计分析又表明,穷人的隔离与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高度相关。 [10]
表6.2 贫穷隔离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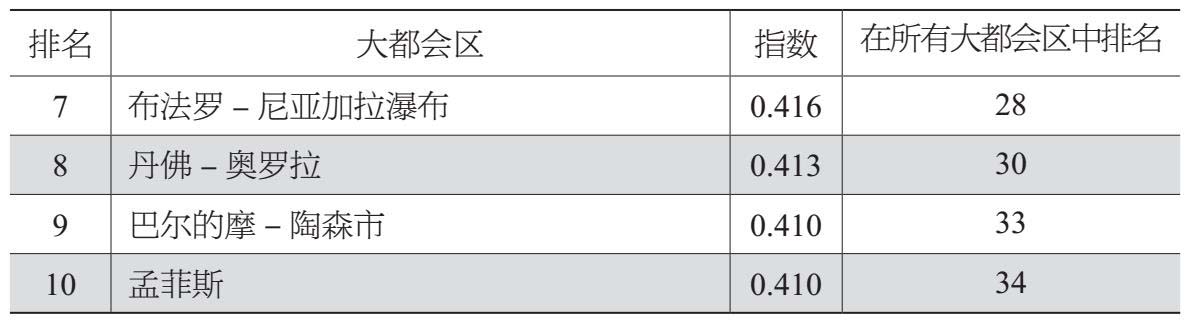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给穷人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1987年出版的经典作品《真正的穷人》中就提出了贫穷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就业岗位更少更差、经济网络和职业网络更落后、学校质量更差、犯罪率更高、同伴圈更糟糕、婚配伴侣选择更少以及更难接触到正面榜样。 [11] 生活在长期贫困社区的人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被孤立于那些能带来经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外。这些劣势导致他们世世代代都被困于贫穷中。
这一现象的反面是如表6.3所示的富人的隔离(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在大城市中,富人隔离程度最高的是老工业城市——如孟菲斯、伯明翰、路易斯维尔、克利夫兰和底特律,以及纳什维尔、哥伦布、夏洛特和迈阿密。但在这里,我们的统计研究再次表明,在规模更大、人口密度更高和高科技行业更发达的城市中,富人的隔离程度更高。 [12]
表6.3 富人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收入隔离的驱动力来自最顶层人群的地理分布。富人比穷人的隔离程度更高。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富人是隔离程度最高的群体。 [13] 这个发现并不意外:富人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占领心仪的地盘,并把自己和弱势群体隔开。这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说的社会的“包厢化”,即富人把自己隔离在远离大众看台座位的私人豪华包厢中。 [14]
除了收入隔离之外,还应该考虑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不同种类的隔离相互强化,它们一直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密集型城市的特征。
人们分类隔离的标准不仅是收入,还有受教育程度。教育有时候也被称作人力资本,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是决定我们收入的核心要素,能强化金钱带来的优势。
低学历人群(高中未毕业)在社会中面临的困难重重。他们的学习速度远低于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也较高。低学历人群隔离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科技中心中的奥斯汀、丹佛、圣迭戈、旧金山和圣何塞,以及“太阳地带”上的菲尼克斯、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休斯敦(见表6.4)。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它们的教育隔离程度也较高。
表6.4 低学历人群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高学历人群(拥有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则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他们的收入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失业率则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大学毕业生的隔离程度在老工业城市最高,包括伯明翰、孟菲斯、路易斯维尔和能源中心休斯敦。洛杉矶排名第三。前十名中还有圣安东尼奥、达拉斯、夏洛特和芝加哥(见表6.5)。整体来看,高学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高科技行业聚集度和创意阶层占比密切相关。 [16]
表6.5 高学历人群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整体教育隔离指标比较了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未毕业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洛杉矶位列榜首,位列其后的四个城市均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其他前十名城市包括科技中心圣迭戈和旧金山,还有芝加哥、哥伦布和夏洛特(见表6.6)。
表6.6 整体教育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职业也很关键。职业为我们带来收入,也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此前我将工作岗位划分为三个大类别:高薪创意阶层、低薪且脆弱的服务业阶层以及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在创意阶层隔离方面,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模式十分清晰地凸显了出来(见表6.7)。洛杉矶排名第一,纽约第五。前十中还有圣何塞、旧金山、奥斯汀和圣迭戈这些科技中心,全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以及三个得州城市:休斯敦、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
表6.7 创意阶层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服务业阶层的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见表6.8)。圣何塞、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圣迭戈、奥斯汀和洛杉矶都在前十名单中,其他两个城市是东北部的费城和巴尔的摩。
表6.8 服务业阶层隔离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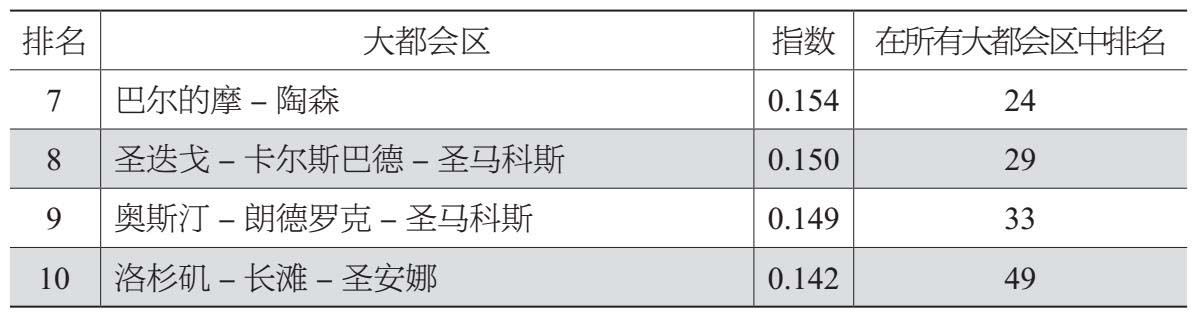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减少,工人阶层的隔离模式与创意阶层很相似。从表6.9中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在工人阶层隔离方面的排名也很靠前。洛杉矶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奥斯汀、达拉斯、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旧金山和圣何塞。纽约和波士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排名也很靠前。
6.9 工人阶层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用包含三个阶层的综合隔离指数衡量整体职业隔离水平,科技中心和超级城市依然位列前茅(见表6.10)。圣何塞排名第一,其次是旧金山、华盛顿、奥斯汀、洛杉矶、纽约、休斯敦、圣迭戈、圣安东尼奥和哥伦布。在这些地方,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均匀分散在城市中的可能性最低,他们倾向于和自己同阶层的人聚集而居。
表6.10 整体职业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三个阶层中最占优势的阶层——创意阶层的地理分布决定了整体职业隔离的模式。原因很简单:创意阶层拥有更多财富,因此对居住地点有最大的选择权。他们选择了最好的地段,把其他两个更弱势的阶层挤到他们挑剩下的地方。
收入、教育和职业隔离的精确动态各不相同,但从统计上看他们彼此密切相关。如果把他们放到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经济隔离的整体地理分布。 [17] 为了揭示这一规律,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发明了两个广泛指标,一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水平,另一个则把这一指标和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结合在一起。图6.1和表6.11(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就绘制了第一个指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隔离的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数。
如图所示,整体经济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是位于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长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湾区附近,得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几个其他地区。知识中心奥斯汀位于经济隔离程度最高城市之首。美国前六大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和费城,都出现在前十名单中。塔拉哈西、图森和安娜堡等大学城也排名靠前。 [18]
为了全面理解经济隔离,我们还分析了影响经济隔离的各种要素。我们把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反映城市重要经济特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高新科技行业聚集方面的数据。
首先,经济隔离与城市地区的面积关系紧密。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城市面积高度相关。 [19] 有超过200个中小型城市的整体经济隔离程度低于那些经济隔离程度最低的大型城市,这一规律基本也适用于每一种单独的隔离形式。图6.2展示了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量)和经济隔离的关系,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表示两者正向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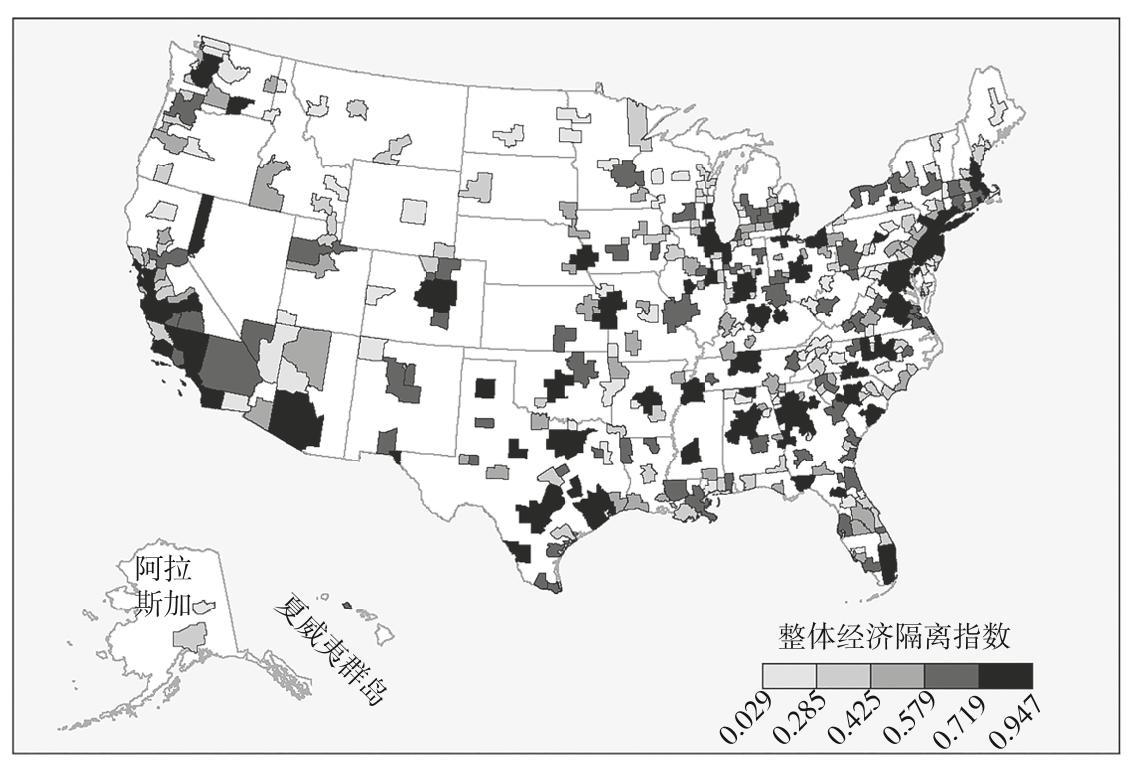
图6.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1)
表6.1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还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人口密度正相关,与另一项反映人口密度的影响的指数——乘坐公共交通通勤者的占比同样正相关。一般来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使用公共交通的通勤方式更普遍,反之人们更倾向于独自驾车上班。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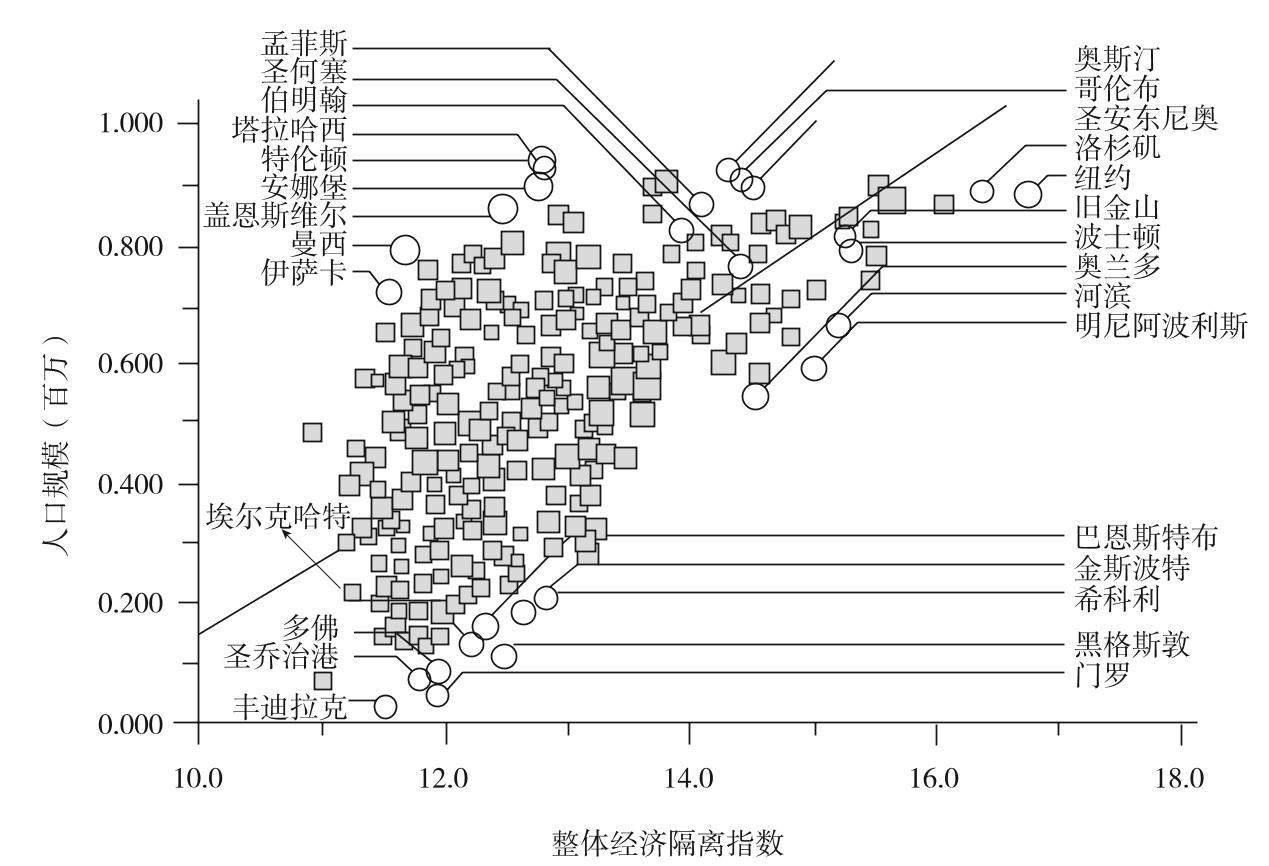
图6.2 城市规模与经济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注: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
经济隔离还是富裕城市的特征:越富裕的地区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和衡量生产力的人均经济产出指标都呈正相关。 [21]
经济隔离和知识型城市的关键特征联系更加紧密,如高科技行业、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经济隔离与高新科技行业和创意阶层的相关性是在我们这次分析中最高的。反之,工人阶层工作岗位越多,能提高蓝领工人工资的工会化率越高,经济隔离程度就越低。 [22]
另外,经济隔离和不平等一样,都与保守地区和自由地区长期分化有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政治自由主义正相关,与政治保守主义负相关。 [23] 虽然这种相关性反映了大型、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的广泛特征,但它仍颇具讽刺意味。
接下来这张地图拓展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图6.3和表6.12展示了全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这一指数综合反映经济隔离、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水平。 [24] 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都排在前列。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纽约排名第一、洛杉矶第二、休斯敦第三、旧金山第四。这一次,美国前六大城市又全部进入了前十大最隔离和最不平等大城市排行榜。在所有城市地区中,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排名第一,其他大学城排名也很靠前,如卡城、盖恩斯维尔、塔拉哈西、达勒姆、雅典、博尔德,以及特伦顿(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城市的面积、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高度相关,它与高科技行业聚集、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的相关性甚至超过了经济隔离本身与它们的相关性。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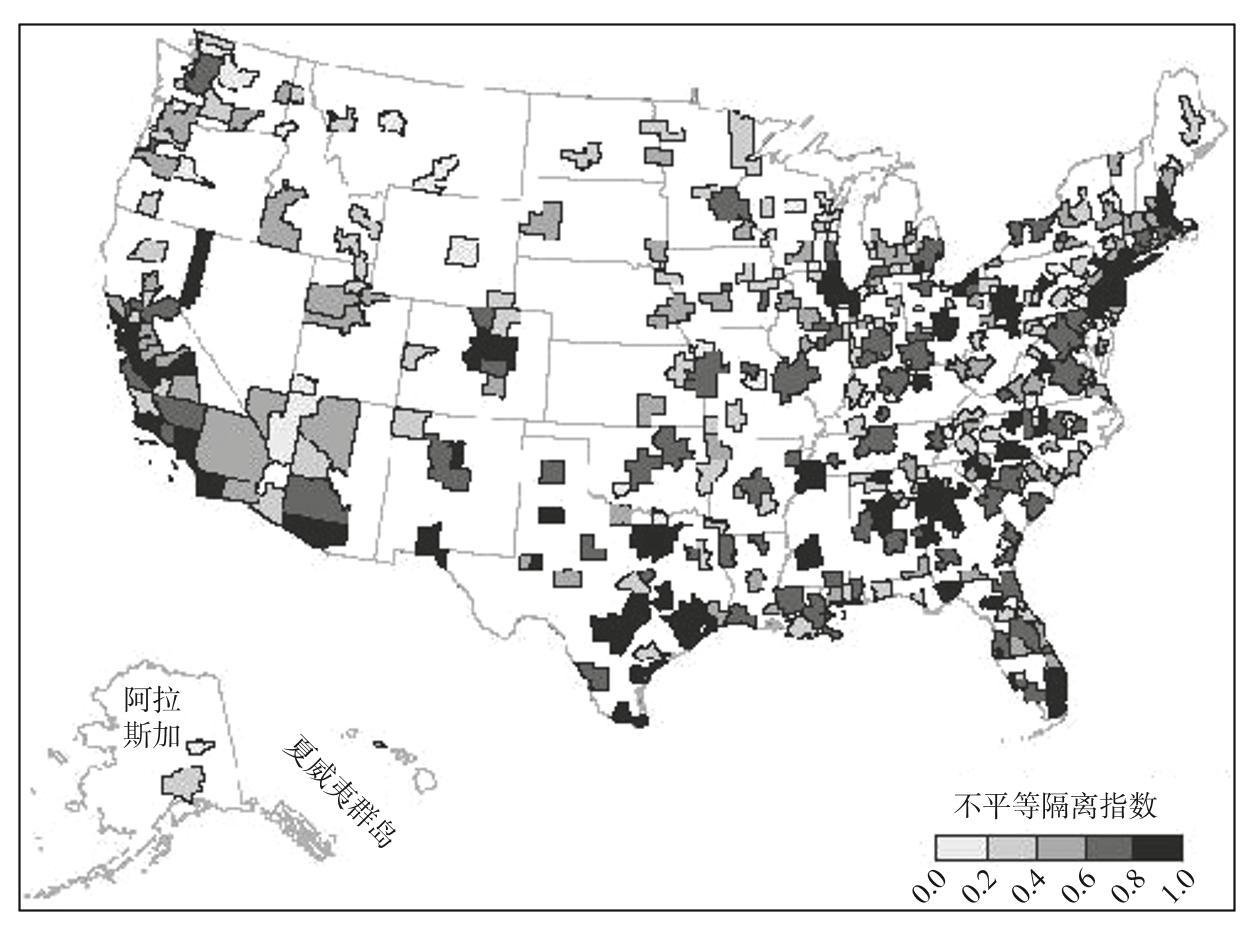
图6.3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1)
表6.12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与经济不平等相伴相生。高度经济隔离的城市地区往往也存在高度收入不平等,而经济隔离和工资不平等的关系甚至更紧密。 [26] 经济隔离与不平等的这种关系已经至少存在30年了。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隔离和不平等都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而加深,即便控制了教育水平、种族、行业和工作结构等因素,两者依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27]
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过去10年,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米兰等很多欧洲城市的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程度都大幅度上升。 [28] 和美国一样,欧洲不断加深的经济隔离也是由富人和优势群体的资源和选择驱动的。
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的结合极其危险。它强化了顶层人群的优势,加剧并持续了底层人群的劣势。它不仅产生了经济资源不平等,还带来了更长期和更畸形的机会不平等。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机会不平等使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25%。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衡量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的传统方法实际上低估了经济分化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的结合带来的破坏性。 [29]
这种机会差异在代与代之间被强化了。大家都知道来自富人区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获得比穷人家庭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如今,父母的收入也是决定年轻人定居地的重要因素。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昂房价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哪怕他们是在高薪的科技行业工作。他们在这些地方买房并获得职业机会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父母。年轻人越来越依靠父母的财富来选择对自己人生前途至关重要的居住地,而没有父母依靠优势的年轻人就可能被关在门外。阶级和居住地两者互相强化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此刻,还在世世代代间不断持续。
今天美国社会的残酷事实就是,贫穷社区永远贫穷,而富裕社区永远富裕。隔离不仅把人困在特定地点,还困住了社区。事实上,2000年的贫困社区中有75%在10年后依然贫困,1990年的富裕社区中有80%在20年后依然富裕。 [30] 我们的邮政编码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命运。
经济隔离不仅是阶级问题,还与种族和美国长期的种族分化密不可分。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到过种族和创意经济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联系。具体来说,在城市地区,少数族裔或非白人的人口占比与高增长的高科技公司聚集呈负相关。最近,我发现黑人在创意阶层中的占比严重不足。黑人虽然占总人口的12%,但只占有8.5%的创意阶层工作。对比之下,占总人口数不足2/3(64%)的非拉丁裔白人拥有近3/4(73.8%)的创意阶层工作。只有28%的黑人工人从事创意阶层工作,而在白人中这一比例为41%。在5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创意阶层工作中白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有37个,而该类工作中黑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只有1个。在大学毕业生和高科技公司更多和更多元化(用移民和同性恋人口衡量)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更高。但在黑人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反而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黑人创意阶层都被吸引去了经济更有活力的地区,那里有更多高技术含量的高薪工作,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 [31]
虽然种族隔离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前的顶峰不断下降,但今天的经济隔离问题和种族仍然存在紧密关联。根据2012年爱德华·格莱泽和雅各布·维格多的一项研究,1970—2010年,美国最大的85个城市中黑人的隔离程度都下降了。 [32] 即便如此,种族和经济隔离仍然密不可分。我的城市地区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黑人人口比例与拉丁裔和亚裔人口比例都呈正相关。相反,该指数与城市的白人人口占比呈负相关。 [33]
这并不意外,种族与阶级仍然是人群和社区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令人意外的是,黑人创意阶层对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有缓和效应。美国城市中黑人创意阶层与收入不平等没有统计相关性,与经济隔离也只存在较小的相关性,这与白人创意阶层或者创意阶层整体的规律都大相径庭——这两者均与收入不平等和隔离呈正相关。 [34] 从政策角度看,这说明促进黑人创意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削弱不平等和隔离现象。鉴于现在创意阶层中黑人比例本来就偏低,实施这一举措更是迫在眉睫。
然而既讽刺又让人忧心的事实是,多元化的城市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隔离问题。我的研究发现,隔离与两个衡量多元化的常见指标正相关:同性恋的聚集和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 [35] 2015年,内特·西尔弗的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整体多元化水平以及它们社区的种族隔离,结果发现种族更多元化的城市,隔离问题也更严重。 [36]
最后,贫困黑人社区就成了种族和经济隔离这套组合拳的最大受害者。黑人生活在集中贫困地区的可能性远高于白人,1/4的黑人住在高度贫困社区,而白人住在此类社区的比例只有1/13。 [37] 另外,城市正在分化为种族集中贫困区域和种族集中富裕区域。根据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15个大都会地区的研究,洛杉矶有129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口,有12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芝加哥则有138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西裔人口,有58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从15个都会地区整体来看,种族集中贫困的地区中,黑人和拉丁裔人口超过75%,而种族集中富裕的地区中,白人人口超过90%。 [38]
在贫困黑人社区长大的人很容易一直待在这种社区。在美国最穷的25%的社区长大的黑人里,有2/3会在同样贫困的社区中养育自己的下一代。讨论种族集中贫困问题的重要著作《滞于其所》(Stuck in Place )的作者帕特里克·夏基曾说:“社区不公平与几代人相关,它像基因背景和财富的代际传递一样,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39]
这种传递同样损害黑人中产阶级,他们比白人中产阶级更可能住在高度贫困的社区及其周边。事实上,约一半黑人中产阶级成长于贫困率超过20%的社区,而白人中产阶级的这一比例仅为1%。 [40] 即便贫困的黑人父母能努力脱贫,他们的孩子也往往会重新陷入贫困。
在种族集中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2015年道格拉斯·马西和乔纳森·罗思韦尔的一项研究显示,成长于最贫困的20%的社区的人和最富裕的20%的社区的人的终生收入差距,基本与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差距相同:近100万美元,精确地说是91万美元。总之,黑人的低经济流动性是他们被隔离并集中于长期贫困社区的结果。 [41]
经济和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危害是阻碍了非优势群体向上的经济流动。根据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等人的一项重要研究,在隔离与经济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42] 来自黑人社区的小孩提升经济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小,成年黑人与成年白人的收入差距中有约1/5来自于他们成长的郡。种族集中贫困给经济流动性和美国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然而有趣的是,切蒂的研究表明,经济阶层流动性最好的地方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大华盛顿地区和西雅图,这几个城市都在向上流动性最好的前20个城市名单中。虽然它们存在严重的隔离与不平等问题,但更有活力的经济、更多高薪行业和工作机会为它们的经济提供了宽阔的上升通道。相反,在人口更少、布局更不紧凑的城市,向上经济流动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因为弱势群体很可能住在离工作和经济机会更远的地方。
不同城市的经济流动可能性差异巨大,我自己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我两岁、我弟弟刚出生时,我的工人阶级父母从纽瓦克搬到了博根郡的北阿灵顿市,并在我们的成长期间不断地提醒我们,当初搬家就是为了给我们铺设更好的人生道路。他们这方面的直觉在切蒂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研究发现在博根郡长大的人拥有更好的人生前途,而纽瓦克则相反。我的父母也挑对了时间,切蒂的研究显示,幼童时期搬到好地方能为孩子带来最大收益。
在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城市,贫困群体除了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更可能活得更长、更健康。切蒂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这样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中,穷人寿命更长;在底特律、加里、托莱多和代顿这几个“铁锈地带”城市,以及拉斯维加斯、塔尔萨和俄克拉何马城,穷人寿命更短。 [43] 如果我们想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改善经济状况、拥有更长寿命和更健康的生活,就必须保障他们不被高住房成本挤出最大、最富裕及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即便如此,所谓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不会神奇地解决集中贫困的问题,比如帮助穷人搬到大城市,甚至是搬到较好社区。向好地方搬迁带来的好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大幅下跌,对青少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种族也是一个因素,白人和拉丁裔小孩比黑人小孩更可能通过搬家获得向上的经济流动。 [44] 这种完全以人为本的政策还会对贫困社区造成巨大伤害:把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和家庭抽走,会导致原本就问题重重的贫困社区更加落后。我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将讨论,如果我们希望打破城市集中贫困的困境,就必须把以人为本的政策与改善社区状况的基于地区的政策结合起来。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虽然各种类别的经济隔离分别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城市更严重,比如“铁锈地带”城市的收入隔离程度更高,“太阳地带”城市的教育隔离更高,然而从整体来看,经济隔离问题在更大、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且更多元化的城市更严重。这个发现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矛盾:那些生产力最高、提供最高薪职位、聚集最多高新科技行业和人才、人口最多、拥有最充裕的公共交通设施、最多元化、政治倾向最自由的城市,却面临着最尖锐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问题。
在这一章和此前的一章,我用综合数据展现了美国城市整体隔离和不平等程度,及其背后作为驱动力的典型城市因素。在下一章,我将用更细分的数据将社区层面的分化现象视觉化,揭示城市和郊区是如何分裂成小范围的集中优势区域和大范围的集中弱势区域的。
[1] 巴尔的摩市的统计数据来源如下。Creative economy: Shade Shutters,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Black income: Joel Kotkin, “The Cities Where African Americans Are Doing the Best Economically,” Forbes,January 15, 2015, www.forbes.com/pictures/femi45jlhh/no-4-baltimore-md.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 “American Urban Inequality: Racially Concentrated Affluence,”Lincoln Land Institute, 2015. Limited economic mobility: Raj Chetty and Nathaniel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and County-Level Estim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5. Crime and violence: Richard Florida and John Roman, “There Are Plenty More Baltimores,” CityLab, May 4, 2015, www.citylab.com/crime/2015/05/thereare-plenty-more-baltimores/392264. Murders and shootings: Baltimore Neighborhood Indicators Alliance, Jacob France Institute, “Number of Gun-Related Homicides per 1,000 Residents,” http://bniajfi.org/indicators/Crime%20and%20Safety/gunhom; 2011 Neighborhood Health Profile:Sandtown-Winchester/Harlem Park, Baltimore City Health Department,December 2011, http://health.baltimorecity.gov/sites/default/files/47%20 Sandtown.pdf.
[2] Elizabeth Kneebone, “U.S. Concentrated Povert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1,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3/31-concentrated-poverty-recession-kneebone-holmes.
[3] 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8).
[4] 关于1980年至2010年间前三十大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上升问题,参见Paul Taylor and Richard Fry, The Ri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2/08/Rise-of-Residential-Income-Segregation-2012.2.pdf.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2010年有28%的低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低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23%;另外2010年有18%的高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高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9%,该报告总结说,“这些数字的上升与长期收入不平等扩大有关,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或混合收入社区的萎缩(从1980年占比85%下降到2010年仅占76%)和低收入社区和高收入社区的双双扩张(前者从1980年占比12%上升到2010年占比18%,后者从1980年占比3%上升到2010年占比6%)”。关于现在住在经济隔离地区的城市居民比例与1970年的对比,参见Tara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no. 3 (2009): 820–844. On the changing share of American families living i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middle-class neighborhoods, 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这项研究将中产阶级社区定义为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到150%之间的家庭,富裕社区为收入超过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50%的家庭,贫困社区为收入低于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的家庭。在中产阶级中,家庭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25%到150%之间的算高收入社区,介于100%到125%之间的是中高收入社区,介于80%到100%的是中低收入社区,介于67%到80%之间的是低收入社区。
[5] 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1, 2016,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 我们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下:在城市地区中,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与工人阶级(0.37)、白人占比(0.34)、政治保守派(与2016年特朗普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的相关度为0.27)成正相关,而这些要素都是经济衰退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与人口密度(-0.22)、创意阶层(-0.20)、多元化(与移民的相关度为-0.46,与拉丁裔的相关度为-0.47,与同性恋群体的相关度为-0.37)和政治自由派(与2016年希拉里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相关度为-0.33)成负相关,这些都是经济活跃地区的基本特征。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还和以下因素负相关:收入不平等(-0.64)、工资不平等(-0.38)、经济隔离(-0.43)和较低阶层人口占比(-0.62)。另外,2000年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和2000年到2014年间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的变化呈显著负相关(-0.48)。
[6] 特定种类的经济隔离指数是绝对度量,数值越高代表隔离程度越高:1代表完全隔离,0代表完全不存在隔离。综合指数则是相对度量,将一个城市地区的各类隔离的程度与其他地区对比。附录提供了对变量、数据和方法论的详细解释,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 Area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7] 贫困线是由美国人口调查局定义的,参见 “Poverty,” 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about/overview/measure.html; US Census Bureau, “Poverty Thresholds,” 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poverty-thresholds.html。
[8] 收入隔离与人口(0.53)、密度(0.44)、创意阶层(0.35)和高科技行业(0.48)正相关。
[9] Carmen DeNavas-Walt and Bernadette D. Procto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US Census Bureau, 2014, 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 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1970–200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10] 穷人的隔离与人口(0.43)、密度(0.54)、创意阶层(0.48)和高科技行业(0.47)正相关。
[11]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2] The segregation of the wealth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pulation (0.38) and high-tech industry (0.26).
[13] 这个结论来自我们计算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数值越高代表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显著高于穷人(分别为0.456和0.324)。实际上,在我们分析的所有群组中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都是最高的。
[14]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 Macmillan, 2012);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Skyboxification of American Life,” Huffington Post, April 20, 2012, 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sandel/what-money-cant-buy_b_1442128.html.
[15] At the national level, see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no. 2 (1991):407–443;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At the city and regional level, see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9); Robert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 1 (1988): 3–42;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Maré,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no. 2 (2001); Edward Glaeser and Albert Saiz, “The Rise of the Skilled City,”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1 (2004): 47–105; James Rauch,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4, no. 3 (1993): 380–400.
[16] 高学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人口规模(0.54)、密度(0.39)、创意阶层(0.43)和高科技行业(0.50)正相关。
[17] 各个隔离指数之间都密切相连,整体隔离指数与收入隔离(0.83)、教育隔离(0.94)和职业隔离(0.95)都紧密相关。
[18] 附录中的表4提供了美国所有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排名。
[19]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人口规模的相关度为0.64。
[20]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密度(0.56)和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49)正相关,与独自驾车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22)负相关。
[2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0.46)和人均经济产出(0.41)正相关。
[22]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高科技行业(0.62)和创意阶层(0.53)正相关,与蓝领工人占比(-0.37)负相关。
[2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4)负相关。
[24] 附录中的表4列出了美国所有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
[25]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其它因素的相关系数如下:与密度的相关度为0.5,人口规模0.6,人均收入0.31,人均经济产出0.42,平均工资0.52,高科技行业0.61,创意阶层0.57,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3。相反,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蓝领工薪阶层在劳动力中的占比负相关(-0.44)。此外,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2)负相关。
[26]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收入不平等(0.52)和工资不平等(0.62)密切相关。不平等与各项单独的隔离指数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很多相关性都非常显著,落在0.40到0.50的区间内。
[27]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28] Tiit Tammaru, Szymon Marcin´czak, Maarten van Ham, and Sako Musterd,eds.,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European Capital Cities: East Meets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15). Also see Richard Florida, “Economic Segregation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s Cities,” CityLab, November 16,2016, www.citylab.com/work/2015/11/economic-segregation-and-inequalityin-europes-cities/415920.
[29] Rebecca Diamond,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3 (March 2016): 479–524; Rebecca Diamond,“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s: Policy and Inequality Implica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SIEPR Policy Brief, July 2014, https://siepr.stanford.edu/?q=/system/files/shared/pubs/papers/briefs/PolicyBrief-7-14Diamond_0.pdf.
[30]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31] 对各种族创意阶层的界定是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显示的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职业的黑人和白人(非拉丁裔)占比数据。黑人创意阶层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如下:密度(0.32)、创意阶层整体(0.39)、大学毕业生(0.31)、高科技公司(0.27)、成年人中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0.34)和同性恋群体占比(0.36)。以上几乎所有因素与黑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都显著低于与白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参见Richard Florida,“The Racial Divide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CityLab, May 9, 2016, www.citylab.com/work/2016/05/creative-class-race-black-white-divide/481749。
[32] Edward Glaeser and Jacob Vigdor, The End of the Segregated Century:Racial Separation in America’s Neighborhoods, 1890–2010, Manhattan Institute, 2012, www.manhattan-institute.org/pdf/cr_66.pdf.
[3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黑人人口占比(0.29)、拉丁裔人口占比(0.24)和亚裔人口占比(0.30)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3)负相关。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它与黑人人口占比(0.30)、拉丁人口占比(0.29)和亚裔人口占比(0.25)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2)负相关。
[34] 黑人创意阶层和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而白人创意阶层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40。黑人创意阶层与我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仅存在微弱相关性(0.20),远低于白人创意阶层与该指数的相关度(0.66)。
[35] 整体隔离指数与同性恋家庭的聚集程度(0.42)和外国长大的成年人占比(0.38)均为正相关。
[36] Nate Silver,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Are Often the Most Segregated,”FiveThirtyEight, May 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he-mostdiverse-cities-are-often-the-most-segregated.
[37] Paul A. Jargowsky, “Architecture of Segregation: Civil Unr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Century Foundation, August 9,2015, http://apps.tcf.org/architecture-of-segregation.
[38] 种族集中贫困地区是指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为非白人,且超过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普查区。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是指超过90%以上的人口为白人,且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收入中位数超过的贫困线4倍以上的人口普查区。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Racially Concentrated Areas of Affluenc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May 2015,www.cura.umn.edu/publications/catalog/niweb1; Alana Semuels, “Where the White People Live,” The Atlantic, April 10, 2015,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4/where-the-white-people-live/390153。
[39] 来自2013年7月与帕特里克·夏基的邮件对谈,也参见他的著作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Richard Florida,“The Persistent Geography of Disadvantage,” CityLab, July 25, 2013, www.citylab.com/housing/2013/07/persistent-geography-disadvantage/6231。
[40] Sean Reardon, Lindsay Fox, and Joseph Townsend, “Neighborhood Income Composition by Household Race and Income, 1990–2009,”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0, no. 1 (July 2015): 78–97.
[41] Jonathan Rothwell and Douglas Massey, “Geographic Effe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conomic Geography 91, no. 1 (2014):3–106; Richard Florida, “How Your Neighborhood Affects Your Paycheck,”CityLab, January 16,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1/how-yourneighborhood-affects-your-paycheck/384536.
[42]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2014):1553–1623;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and Nick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 no. 5 (2014): 141–147; Chetty and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ay 2015.
[43] Raj Chetty, Michael Stepner, Sarah Abraham, Shelby Lin, Benjamin Scuderi,Nicholas Turner, Augustin Bergeron, and David Cutl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5, no. 16 (April 26, 2016):1760–1766.
[44] Chetty et al.,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also see Pat Rubio Goldsmith,Marcus L. Britton, Bruce Reese, and William Velez, “Will Moving to a Better Neighborhood Help? Teenage Residential Mobility, Change of Context,and Young-Adul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rban Affairs Review (March 4, 2016) online edition; Molly W. Metzger, Patrick J. Fowler, Courtney Lauren Anderson, and Constance A. Lindsay, “Residential Mobility During Adolescence: Do Even ‘Upward’ Moves Predict Dropout Ris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2015): 218–230.
美国的阶级分化早就嵌入了各种居住地的分布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都住在碧绿的郊区,如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底特律的格罗斯波因特、费城的布林莫尔或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抱负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住在更小、人口更密集、离市中心更近的郊区,如长岛的莱维顿或我长大的新泽西州的北阿灵顿。穷人和真正的弱势群体则挤在市中心的贫民窟,如芝加哥南区、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或离我的出生地不远的纽瓦克部分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郊区一般都较富裕,社会向上流动性很强,并且以白人居民为主,而市区则被挖空,经济萧条,少数族裔和贫困居民越来越多。
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一直认为,阶级身份诞生于工厂车间等工作场所,然而,今天美国的阶级划分不仅与工作类型挂钩,还与我们的居住地息息相关。居住地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通勤距离、经济机会、孩子上的学校、健康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阶级和居住地的关系吸引了来自各个意识形态的评论员的关注。查尔斯·默里在他2012年的著作《走向分裂》(Coming Apart )中比较了两个不同阶层的社区,论证了美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分化的两级: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外的贝尔蒙特郊区的外向型富裕居民,以及位于费城菲什敦社区的落后的、被疏离的内向型工薪族居民。罗伯特·帕特南在其2015年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以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衰落为案例,研究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美国梦的消失。 [1]
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已经不再遵循富郊区、穷市区的老规律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大量高薪知识工人、富人和年轻人已经重返市中心,而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则被迫迁往郊区。这种美国地理划分的反转现象有时被称作“大逆转”。 [2]
但是当代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实际上与这两种模式都不同,它正被重塑为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模式,我称之为拼布城市。虽然它的具体特性在每个地方都各不相同,但这种新型阶级地理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城市分裂为紧密结合的集中优势区域和面积更大的集中劣势区域,它们在市区和郊区中纵横交错。
在上一章中我用总体数据描述了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在这一章中我会用更细分的数据来识别新分化是如何嵌入城市地区的,并将其视觉化。其他相关研究要么就是追踪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如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要么就是根据收入将人划分为不同群体(如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我的研究框架与他们不同,我在地图上画出了三种主要阶层人群的居住地点。我和我的团队通过详细数据确定各个人口普查区的主导阶层,是高薪创意阶层、低薪服务阶层还是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我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十几个发达城市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包括超级城市、科技中心、蔓延扩张的“太阳地带”城市和去工业化的“铁锈地带”地区。 [3]
虽然每个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阶层特征,但从整体来看有四种拼布城市模式。
在第一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重新占领了市中心,同时在郊区也保持高度聚集。状况稍差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要么被挤到了市区的其他区域,要么被挤到郊区甚至远郊的边缘地带。这种模式出现在纽约、伦敦这样的超级城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这样的知识中心,以及多伦多和芝加哥。
在第二种模式中,创意阶层留在郊区,很少回到市中心。这种模式出现在“太阳地带”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以及“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匹兹堡和克利夫兰。
在第三种模式中,整个城市地区被一分为二,优势创意阶层和弱势服务阶层在市区与郊区中分别占据完全不同的街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属于这一类型。
在第四种模式中,富裕的创意阶层占领了一些独立的小型聚居区,弱势阶层则围绕他们而居。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创意阶层沿着海岸线的市中心地带,围绕着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很多小型聚集区。
创意阶层对地点的选择特权塑造了以上各个类型的新型拼布地理模式,而以下四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他们对聚集地的选择。
第一个因素是离市中心的距离。纽约和伦敦这两个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这几个知识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最为强烈,在很多城市地区也能看到一定程度的重返城市现象。
第二个因素是到公共交通点的距离。创意阶层喜欢围绕地铁站和公共交通线路而居,这样可以节省通勤时间,避免长距离开车通勤。这一因素对于住房成本高昂而公共交通发达的人口密集型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尤其重要。
第三个因素是到主要大学和其他知识机构的距离。以前很多人住在大学附近只是权宜之计,并不久留,比如大学生在读书时住在学校附近,毕业后就会离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城市的大学,如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城市衰败的影响变成了封闭的孤岛。而今天,城市大学和其他知识型机构附近的社区成了创意阶层的居住选择,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与学校并没有直接联系。 [4]
第四个因素是到自然景观的距离。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城市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还喜欢最美观的地方,比如靠近公园、环山,特别是临水临海的地段。这一规律在创意阶层沿海岸线而居的洛杉矶和迈阿密最为显著,也适用于其他城市的临水老工业区域,以前的老工厂仓库被改造为满足创意阶层需求的住宅、商店、画廊和办公楼。
为了全面理解拼布城市的模式,我们先回顾一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它们为我们理解如今的阶层地理现状奠定了基础。
在绘制新型阶层地理分布图前,我回顾了20世纪初期城市学家罗伯特·埃兹拉·帕克及其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的开创性著作。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要,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城市现状的看法。即便他们的模型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今天的现实情况,但他们对早期工业城市形状和模式的开创性描绘,为我们理解当今新型阶级地理现状提供了基本方法论。 [5]
帕克的经历太特别了,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他于1864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哈维维尔,它位于斯克兰顿附近的一个无烟煤矿区。在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前,他只是一名铁路工人。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然后重返学术界,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师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随后他去德国深造,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格奥尔格·齐美尔是极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1903年的经典著作《大城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的作者。帕克对非洲(他曾短暂地担任刚果改革协会的公关人员)和美国(曾协助成立黑人城市环境委员会,即现在的城市联盟)的种族关系问题十分着迷,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和布克·华盛顿一起用10年时间写完了《最底层之人》(The Man Farthest Down )。
帕克最后去了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对芝加哥展开深入研究,包括工厂、屠宰场、红灯区、新摩天大楼、工人阶级社区、贫民窟和快速发展的郊区。他是城市人种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方面的先驱,对城市经济学也有所涉猎。他发表了关于流浪汉、少年犯罪和高贫困社区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就是他的实验室。
帕克就像生物学家研究器官形态和结构一样研究城市的结构。对他来说,城市远不仅是物质特征、建筑和交通干道的集合,它还是人类活动的组织机制。帕克和他的同事恩斯特·伯吉斯和罗德里克·麦肯齐在1925年合作出版的经典丛书《城市》(The City )中写道:“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或人工构筑物,它与人类的生命活动休戚相关。城市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性的产物。” [6] 城市由负责组织各类人类活动的独立空间和社区构成,用帕克的话说就是“由一些相邻但互相不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镶嵌画”。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及其主要构成,帕克和他的同事绘制了芝加哥的各类城市空间分布图,包括以下几类:商业区,工厂、仓库等工业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住宅区。
他们用来理解和视觉化城市地区基本结构的研究框架十分具有影响力。在这一框架下,城市的各种功能分区呈同心圆带状分布。圆心是中心商业区,有高层写字楼、法院等政府机关、商场、主要运输枢纽,其他功能分区围绕圆心向外层层扩张。圆心向外一层是工业区的工厂、屠宰场、仓库等建筑,也被称作“过渡地带”。再向外一层是工人阶层住宅区,这里密集杂乱地分布着各种公寓楼、酒吧和公共浴室,很多建筑都在工业区能听得到声音(也能闻到味道)的范围内。离市中心距离越远,人口密度越小。再往外一层是中产和上层阶级住宅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有带大停车场的大别墅(见图7.1的左图)。
约10年后,芝加哥大学博士和经济学家霍默·霍伊特在这一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他认为城市的功能分区并不是呈齐整的同心圆分布,而是沿着交通主干道呈楔形或扇形分布(见图7.1的中图)。他在1939年为联邦住房管理局做的研究中分析了约60个美国城市地区,展示了城市中最有优势的群体是如何通过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来影响城市轮廓的。他认为,“在考虑城市发展问题时,高租金地区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他还把高租金区域称作“有利地区”。高级住宅区向郊区迁移的势头很猛,“高租金或高档住宅区向城市外围转移几乎是必然现象,富人不太可能会搬回以前被他们放弃的老住宅”。他写道:“田野、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乡村庄园就像磁铁一样,把高档社区吸引到外围有免费开放空间的地方。”约10年后,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昌西·哈里斯和爱德华·厄尔曼对霍伊特的模型做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更加分化的城市多核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城市有多个商业和住宅中心(见图7.1的右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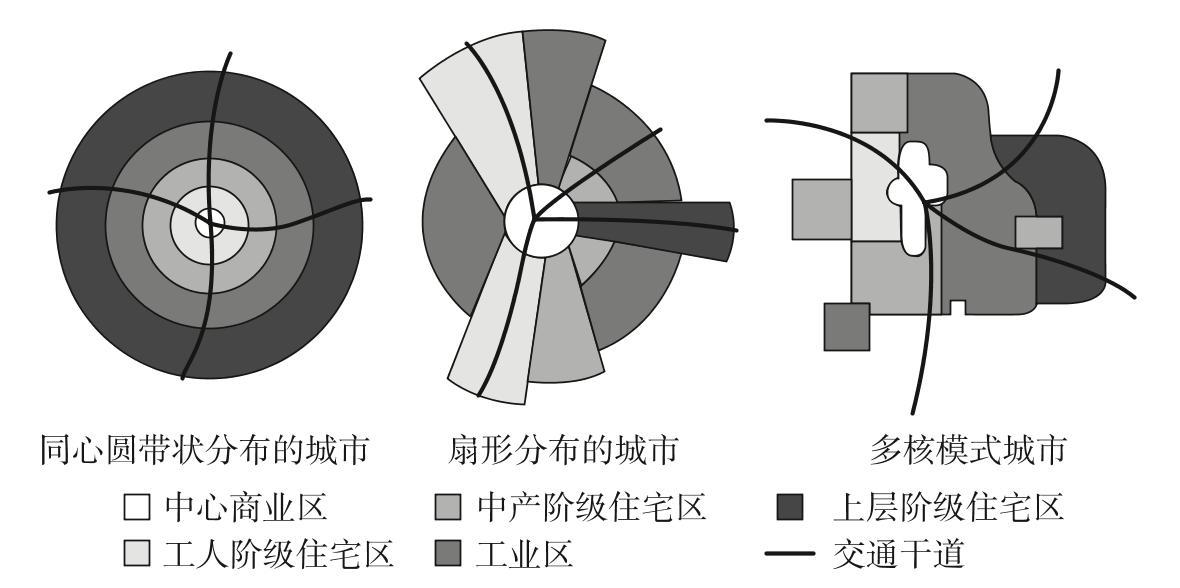
图7.1 芝加哥大学研究的城市空间分布模型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发显著的向外发展模式让市中心失去了很多核心经济功能。1959年,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和雷蒙德·弗农在研究大纽约地区的《解剖城市》(Anatomy of a Metropolis )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他们将它称为“逃离高密度”。他们说,工商业活动和城市居民正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这一趋势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卫星城的出现,郊区卫星城的办公园区和购物中心基本取代了日益荒芜的市中心。 [8]
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之初时,城市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开始返回市中心,而穷人则被迫迁入郊区。随着形势的变化,城市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新模式,与现有模型都不同。有的市区变富了,有的郊区变穷了,并且新模式不只改变了地区。我将以一些大城市为例,探索今天新拼布模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重塑市区与郊区的主要因素。
第一种模式来自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超级城市纽约和伦敦,科技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五大湖区的复兴城市芝加哥和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地区的特征是面积大、人口多、创意阶层高度聚集(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域),并且公共交通发达,这些特征都有利于主要社会经济阶层地理结构的形成。
在纽约市,创意阶层已经占领了整个市中心,从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区、翠贝卡、苏荷区、格林尼治村、切尔西、中城,到上东区(见图7.2)。在布鲁克林,创意阶层的活动范围原来几乎仅限于与曼哈顿下城的相邻部分地区,不过现在也在向其他地方辐射。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纽约市,还出现在长岛、新泽西和韦斯特切斯特郡。该地区只剩少数几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它们主要分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帕塞伊克地区附近,都离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很近。蓝领社区消亡的速度如此之快,很难想象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有巨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和工人阶级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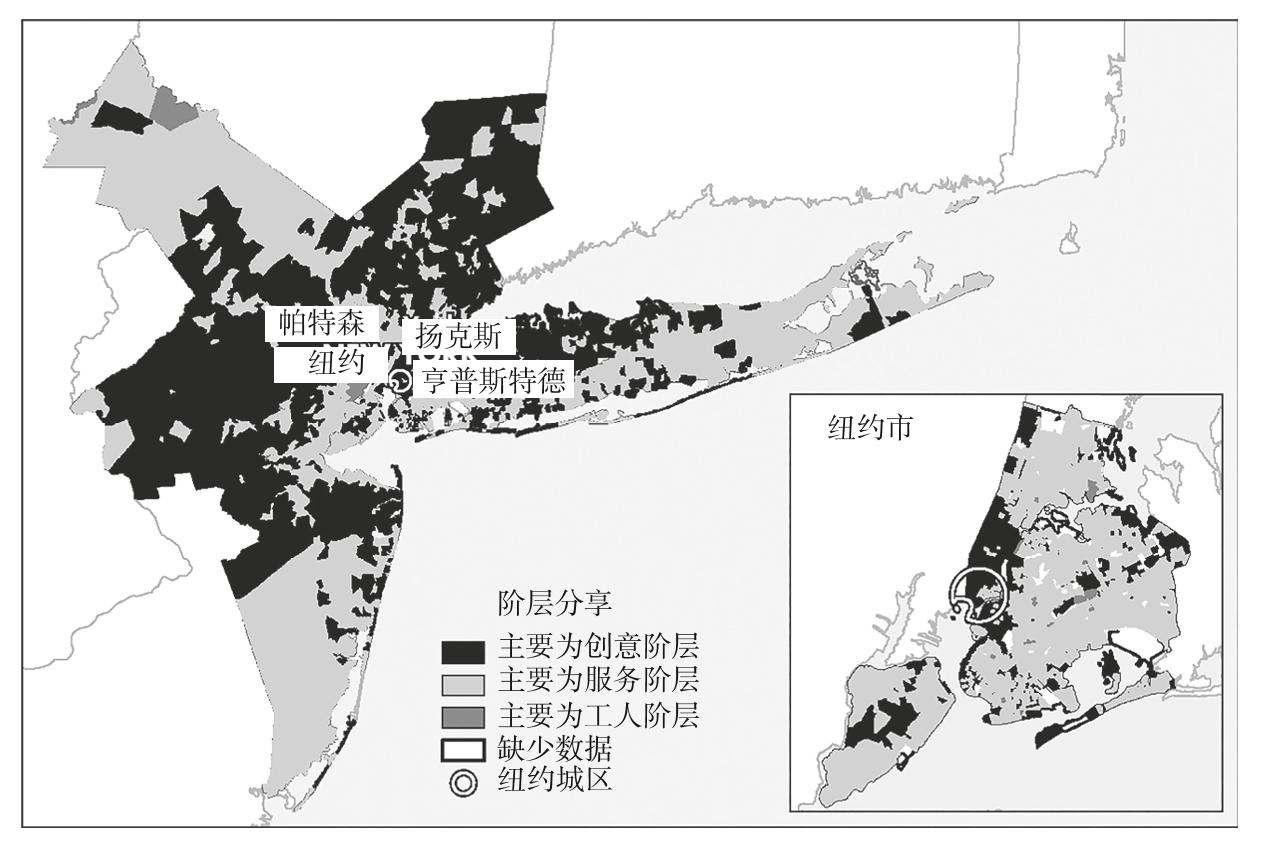
图7.2 纽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伦敦地区的创意阶层则更加聚集在市中心。在包括肯辛顿、切尔西、伦敦市、卡门和国会山的内城地区,创意阶层人口占比达到80%(见图7.3)。大部分服务阶层都被迫搬到城市边缘,主要分布在城市西北、东北和南部的三片大区域。还有一部分服务阶层聚集在泰晤士河南边、更靠近市中心的一片地区。但出人意料的是,伦敦没有一片区域的主要人口构成为工人阶级,要是马克思知道这一发展趋势的话一定会大为震惊,毕竟他曾经在大英博物馆花了数十年时间书写工人阶级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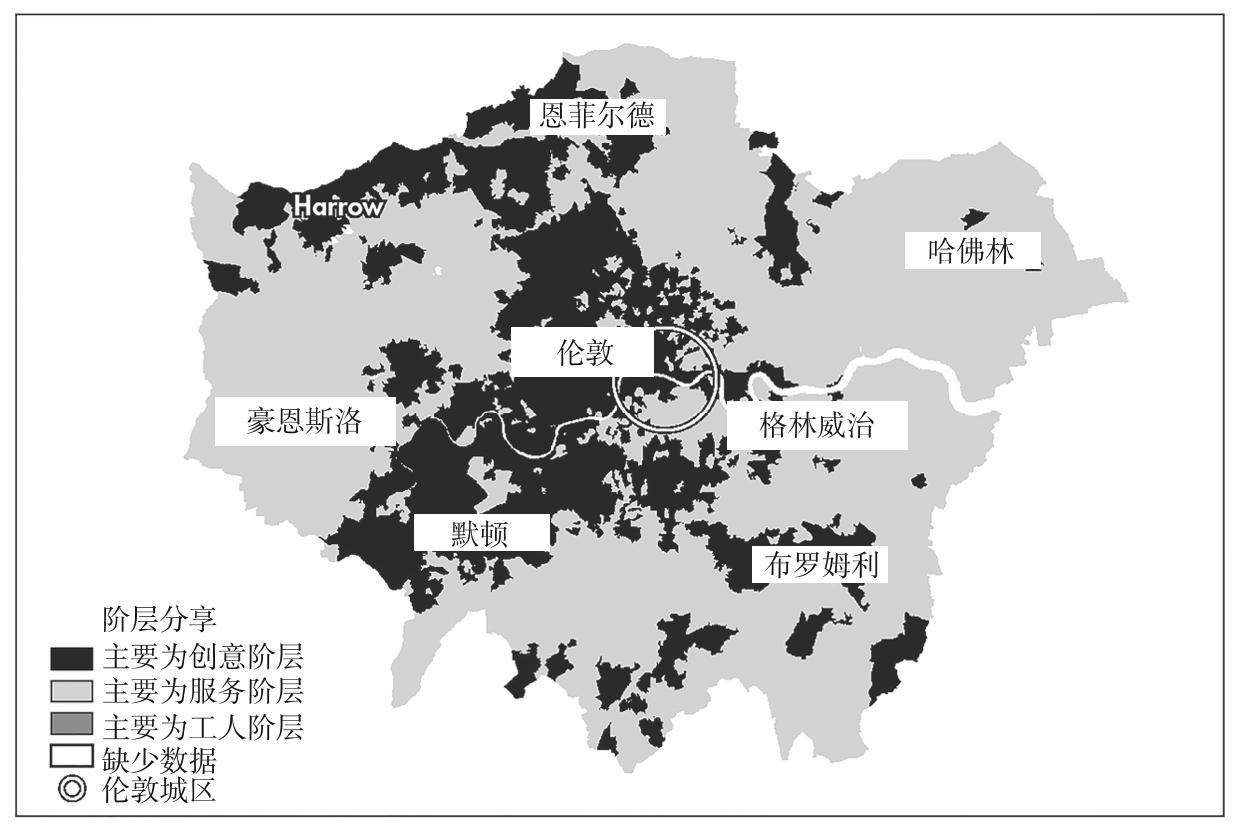
图7.3 伦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基于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邻里统计和人口普查结果。
芝加哥地区如今的阶层地理状况与帕克当时写的非常相似。与纽约和伦敦一样,芝加哥的创意阶层也重新回到了市中心,对老工厂和仓库进行改造重建,并住进了附近的老蓝领阶层社区,如芝加哥小熊球队的主场瑞格利球场的所在地威格利维尔(见图7.4)。创意阶层也在郊区聚集,如芝加哥大学附近的海德公园。他们还喜欢市中心与郊区的湖滨地区,如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埃文斯顿。服务阶层社区也在市区与郊区均有分布。大量弱势群体还留在城市中,芝加哥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聚集社区中有9个都在芝加哥市。其中有4个社区位于市区西南部的恩格尔伍德,这个面积仅3平方英里 [01] 的地区贫困率超过40%,是全市贫困率的两倍。服务阶层还在市区和郊区创意阶层社区的中间地带聚集,以及芝加哥地区的远郊。这个曾经的老工业城市已经几乎没有工人阶层聚集地了,工人阶层现在分布在更远的乔利埃特市和加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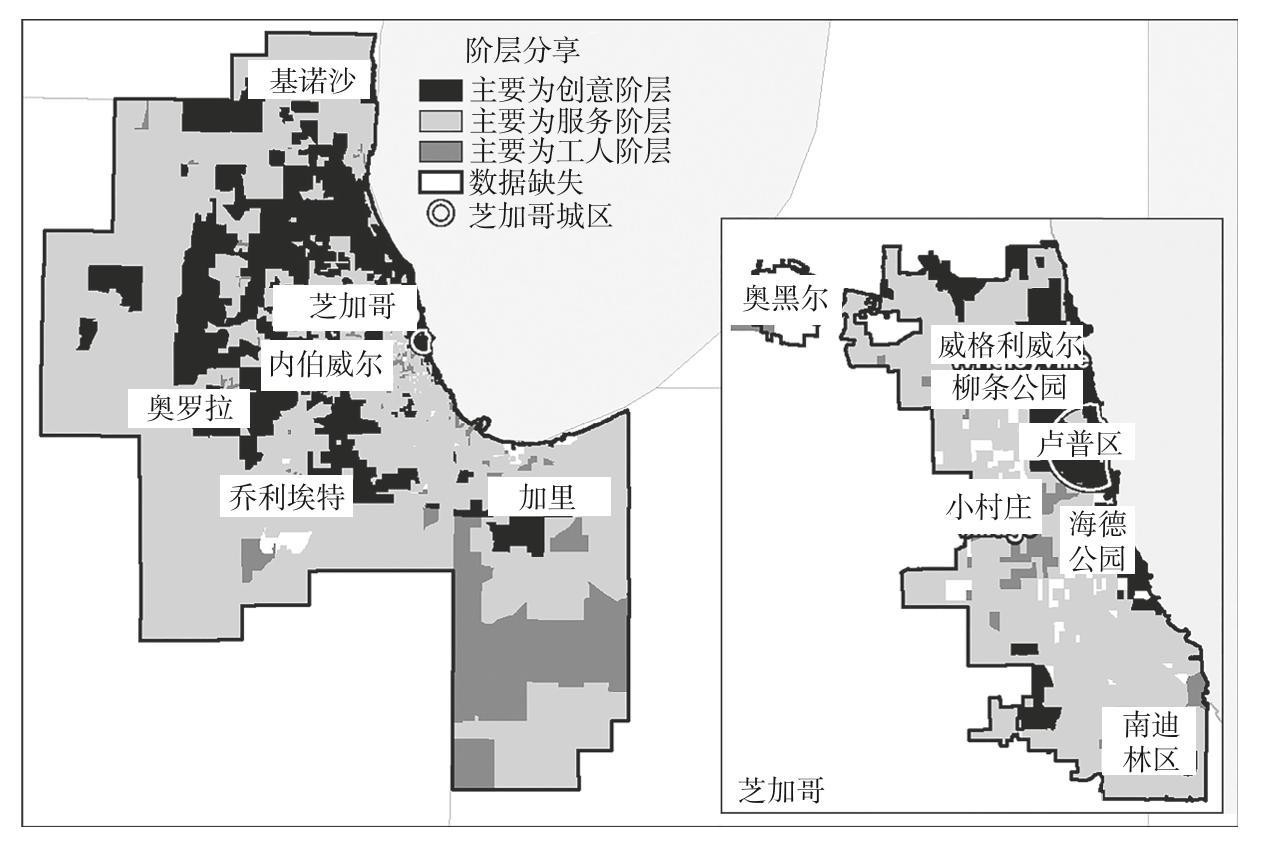
图7.4 芝加哥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我的第二故乡多伦多地区,创意阶层紧密集中在市中心的多伦多大学等几所学校和主要医疗机构附近,并以市中心为起点沿着主要交通路线呈倒T字形向外拓展(见图7.5)。在东西方向,他们沿着湖滨和交通干线穿过快速绅士化发展的皇后西区,向郊区的密西沙加市和高端湖滨小镇奥克维尔拓展;在南北方向,他们向北边郊区的万锦市和皮克林市拓展。服务阶层则被挤到了更外围的地区。体现在我的地图上的多伦多发展模式与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大卫·赫尔恰斯基早前发现的模式一致。他的研究发现,多伦多已经被分成了三块:市中心和主要交通干道沿线的少量富裕社区、离市中心和交通干道更远的大量较贫困社区、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社区。 [9] 多伦多地区也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零散分布在城市西边的郊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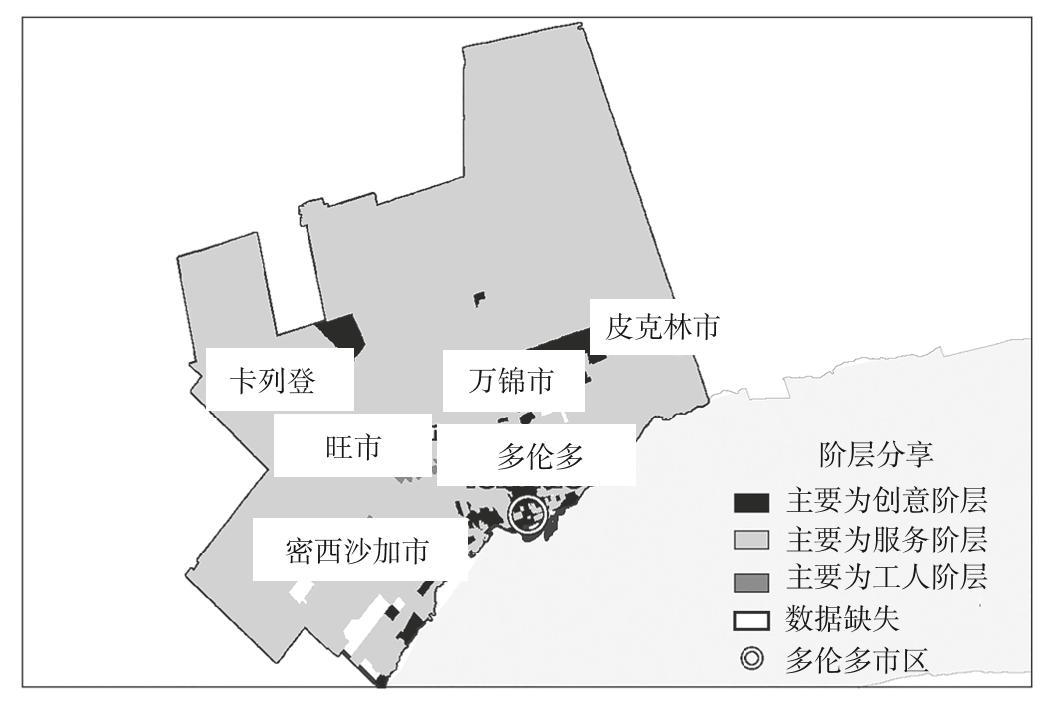
图7.5 多伦多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这一规律也出现在发达的科技中心城市。例如,旧金山地区的创意阶层大量聚集在市中心、海港区、旧金山大学、传统高档社区太平洋高地与俄罗斯山、海特、卡斯特罗以及新绅士化的使命湾和索玛科技区(见图7.6)。不过和其他城市一样,旧金山的创意阶层也在向郊区蔓延,他们占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边地区、北部的马林郡、东南部和西南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周边地区。他们还大量分布于东湾,旧金山地区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奥克兰的上洛克里奇有最大的创意阶层社区,同时奥克兰还有大量服务阶层人口,他们中有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奥克兰和湾区,服务阶层生活在创意阶层社区之间和更远的郊区边缘。在旧金山市,服务阶层聚集在某些最富裕的社区外围。旧金山地区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8个都在日益繁荣的湾区,其中大部分都在市中心附近。马林郡北部和奥克兰东部的边缘地带也有大片服务阶层社区,分布在从奥克兰、费利蒙、门罗公园到硅谷中心东帕洛阿托的长条带状地区。旧金山地区几乎已经没有工人阶层社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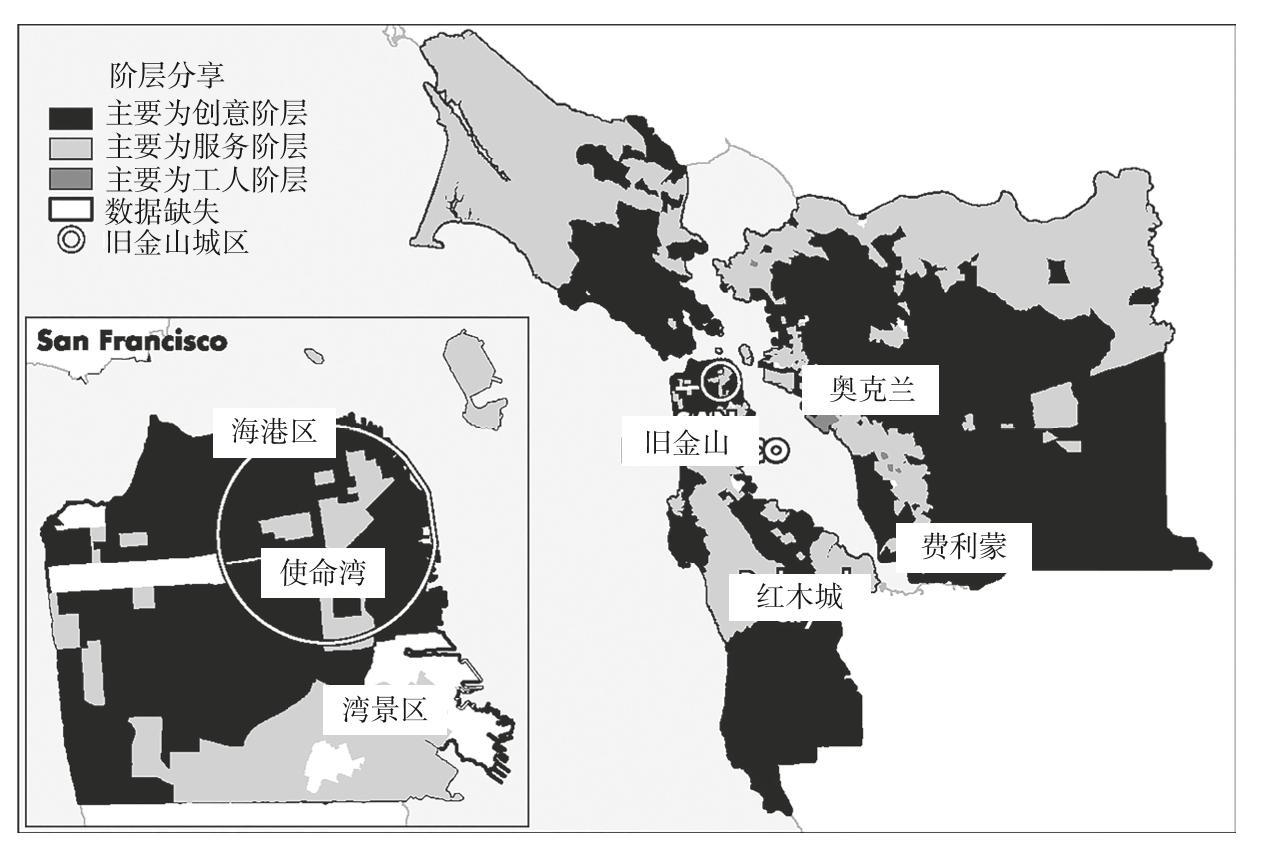
图7.6 旧金山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波士顿的创意阶层也聚集在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从金融区和法尼尔厅到高端的灯塔山和后湾地区、同性恋社区中心南角区,以及芬威-肯莫尔区(见图7.7)。历史学家萨姆·巴斯·华纳在半个世纪前的经典著作《电车郊区》(Streetcar Suburbs )中就提到过,交通设施塑造了波士顿的城市形态。 [10] 红线地铁穿过剑桥,它的沿线车站周边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创业公司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也广泛分布于郊区。在西边,一个主要创意人口聚集地从剑桥外一路延伸到贝尔蒙特、列克星敦、康科德及更高端的牛顿、韦尔斯利和萨德伯里,其中大部分社区都通过交通系统与市中心相连。声名远扬的128号公路科技长廊沿线也有大量创意阶层聚居地。 [11] 还有很多创意阶层分布在北部海岸线沿线的高端社区,包括海边的曼彻斯特、斯旺普斯科特和马布尔黑德。波士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波士顿市,4个在剑桥,3个位于波士顿学院附近地铁绿线上的牛顿。服务阶层则聚集在波士顿市中心外的狭窄带状地带,并向北延伸到马布尔黑德,向南延伸到昆西,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位于城市地区边缘的大型聚居地。波士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9个都在波士顿市,主要分布于南波士顿的传统黑人社区洛克希伯里和东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附近。虽然20世纪中期波士顿还是领先工业城市,但它现在只有不到15%的蓝领工人阶级人口,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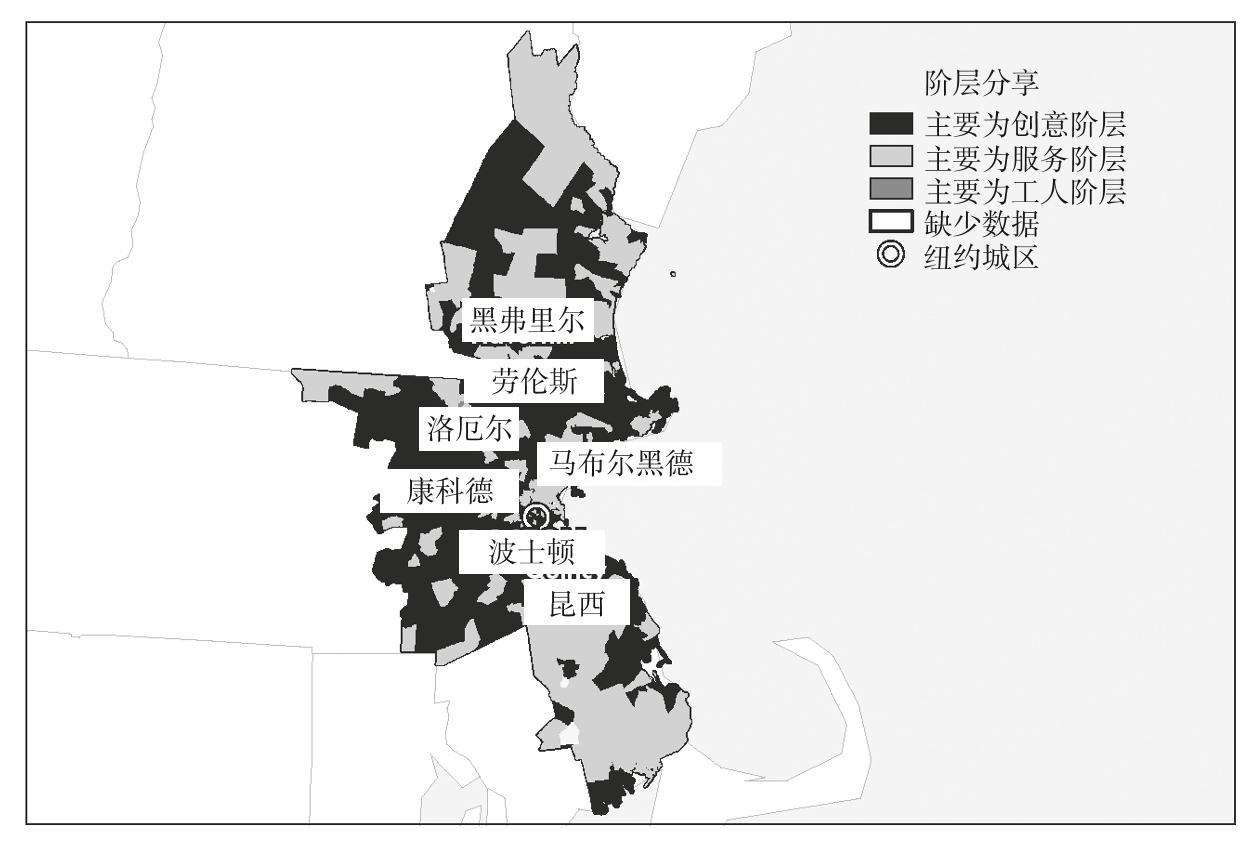
图7.7 波士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华盛顿的创意阶层横跨市区与郊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近一半,位居全国前列(见图7.8)。创意阶层聚集地主要包括乔治敦、克利夫兰公园、西北区、市中心和国会山等绅士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创意阶层还延伸至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和亚历山大这些近郊地区,还有弗吉尼亚北部的费尔法克斯、马纳萨斯和利斯堡,以及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和弗雷德里克等远郊地区。华盛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是亚当斯摩根、克利夫兰公园和拉尼尔高地。其他7个在交通方便的近郊地区,其中4个在阿灵顿,2个在贝塞斯达,1个在亚历山大。哥伦比亚特区沿中轴线可以划分为东西两片地区,创意阶层聚集在西北部,服务阶层聚集在东南部,并拓展到黑人占比65%的乔治王子郡,这里黑人人口占比为65%。华盛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7个在哥伦比亚特区,还有2个在乔治王子郡。大华盛顿的服务阶层工人占比为40%,是美国少有的几个服务阶层人口少于创意阶层人口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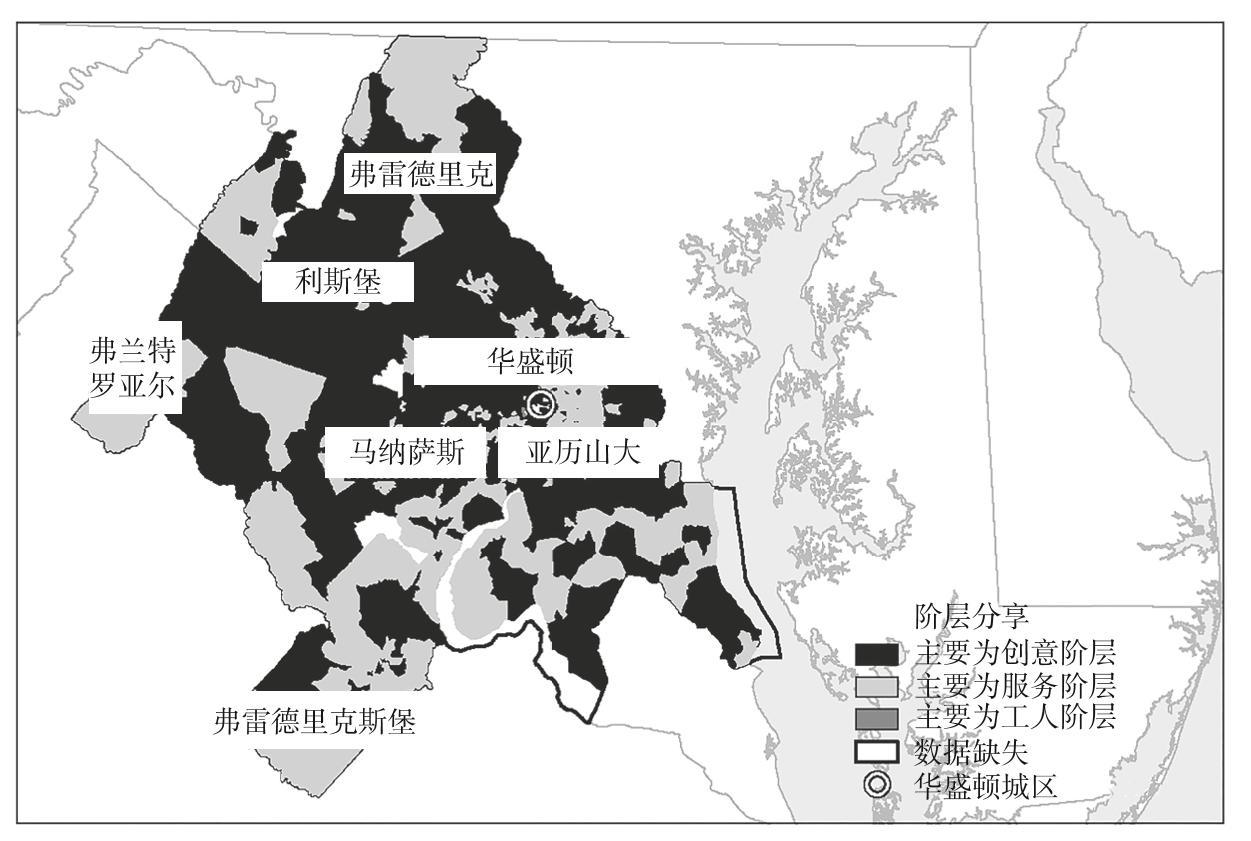
图7.8 华盛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二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仍然留在郊区。这种郊区模式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等“太阳地带”城市,以及底特律和匹兹堡等“铁锈地带”城市。“太阳地带”城市的创意阶层一直以来都偏好高端的郊区社区,虽然通勤更辛苦,但仍然比前文中提到的第一种模式城市居民更依赖汽车。在“铁锈地带”城市,流行的“白人群飞”现象早就掏空了市中心,因此创意阶层也一直更青睐郊区。在大底特律地区等部分城市地区,20世纪早期沿着河岸和铁路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区也能帮助重塑城市,比如让城市变得更加适宜步行,或者被重建为购物、餐饮和夜生活一体化的功能区。尽管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这些城市普遍比上述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面积更大、分布更松散、更依赖汽车,并且公共交通也更不发达。重返城市的浪潮没有大规模发生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创意阶层也更小。
亚特兰大的创意阶层占领了市中心东北部的地区,包括市区的市中心、中城和巴克黑德以及北部郊区(见图7.9)。该地区的东南部则基本被服务阶层占据,只有零星几个创意阶层社区。亚特兰大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7个位于亚特兰大市,大多数都是贫困黑人社区。工人阶层则分布在城市郊区的偏远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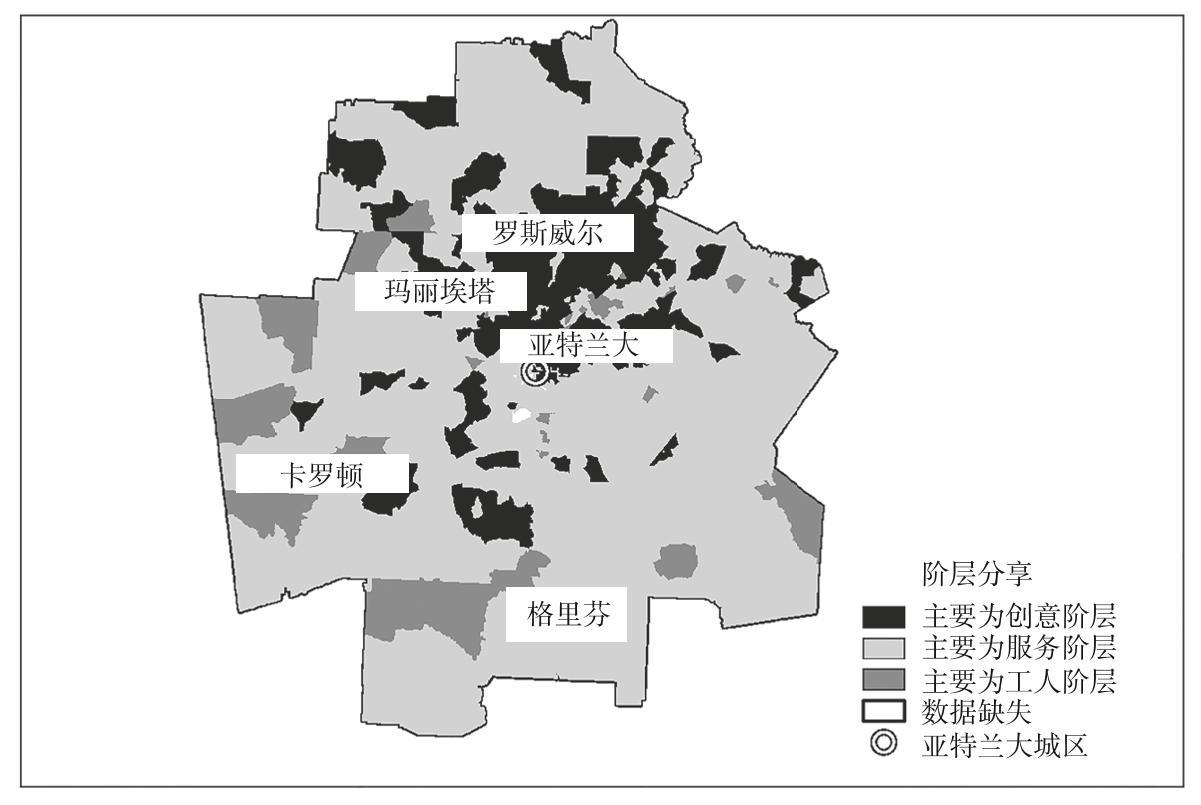
图7.9 亚特兰大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达拉斯的创意阶层集中在北部郊区,包括普拉诺、弗里斯科和欧文,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见图7.10)。该地区的南部主要是服务阶层的地盘,也有少数几个创意阶层社区。市中心南部的三一河也是一条不太明显的分界线,西河岸是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社区,东河岸是创意阶层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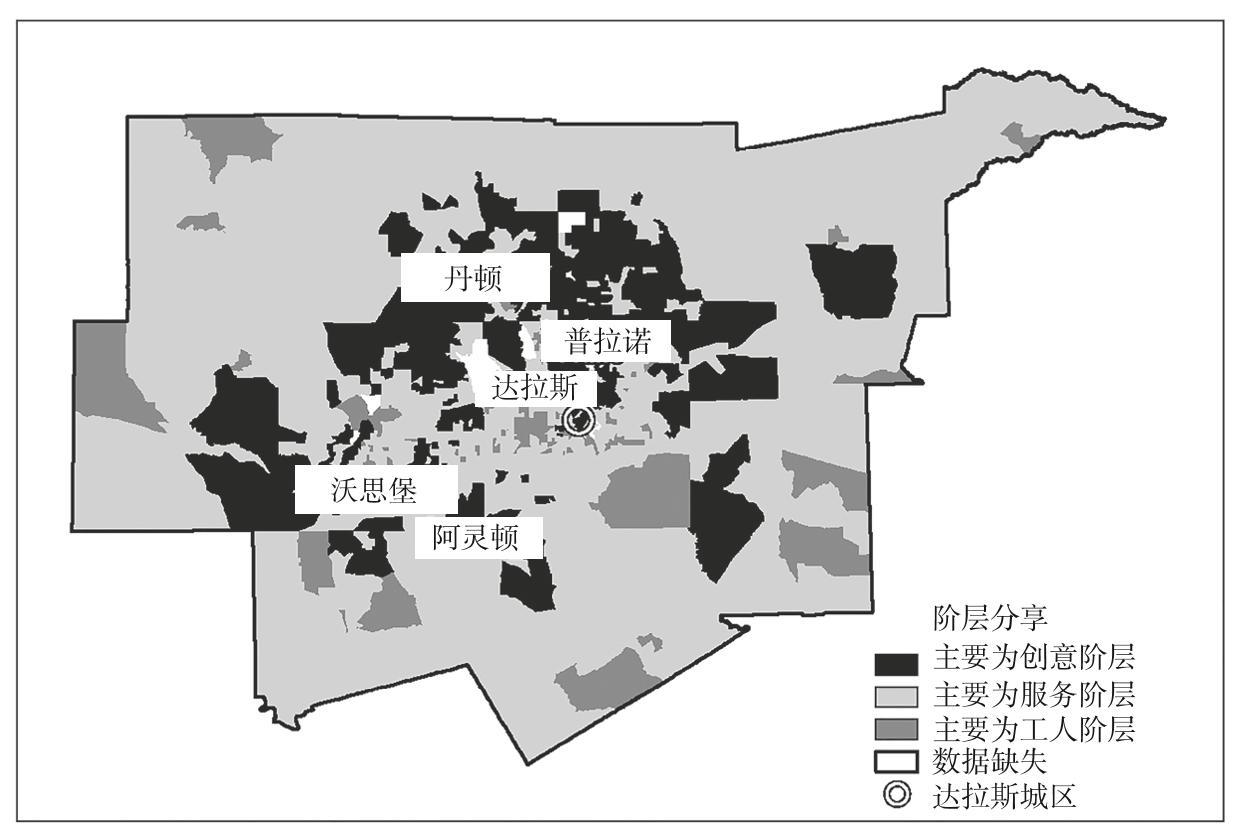
图7.10 达拉斯-沃思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休斯敦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两个环带,一个是从北部伍德兰斯到西南部舒格兰的大郊区环带,另一个是围绕市中心的小环带(见图7.11)。即便如此,该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仍有9个在休斯敦市,其中7个在莱斯大学附近的高端社区。服务阶层主要分布在两大片地区,一个位于市中心和近郊创意阶层聚集地的中间地带,这里覆盖了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9个。其他服务阶层人群则分布在更偏远的郊区。休斯敦的工人阶层主要集中在休斯敦港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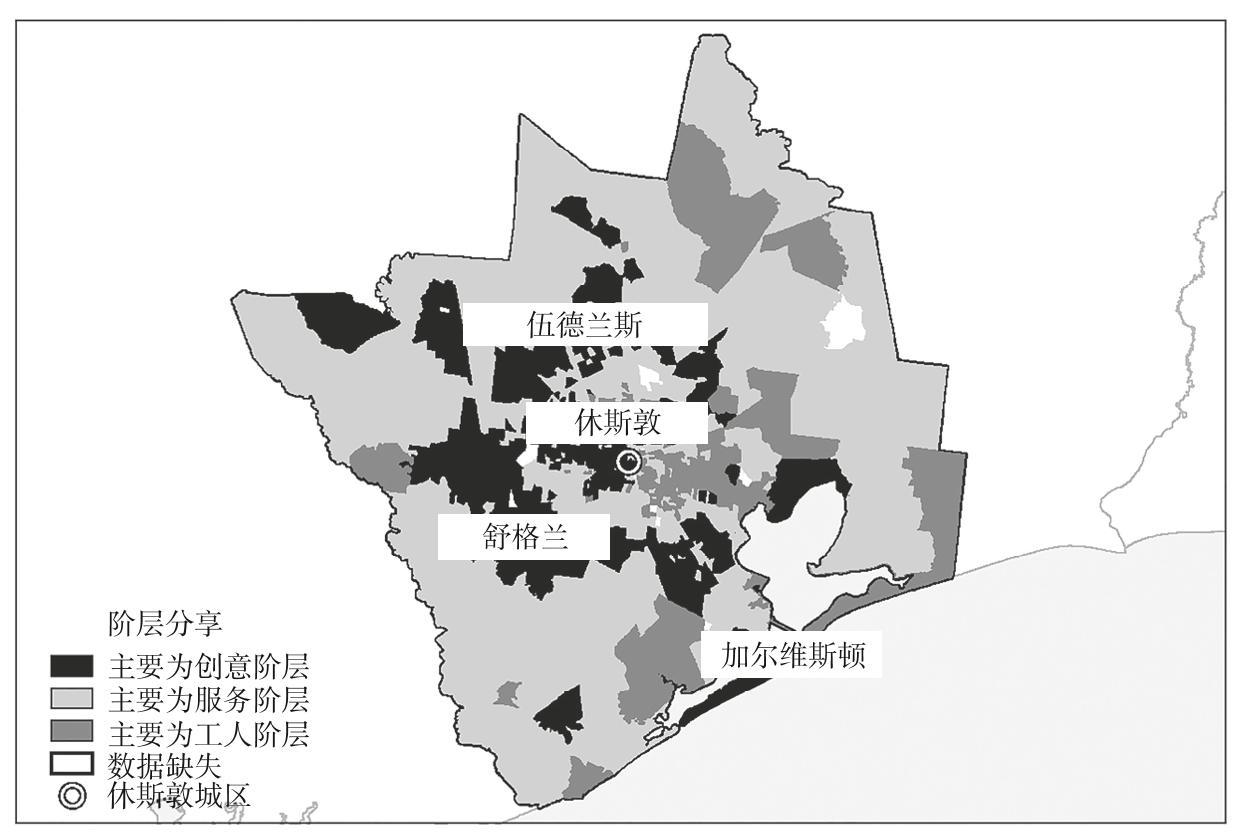
图7.11 休斯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纵观从南到北的“铁锈地带”城市,我们都发现了相似的郊区中心化模式。“太阳地带”城市实际上是围绕公路发展的,但是“铁锈地带”城市在经历了20世纪的“白人群飞”浪潮并且市中心被掏空后,城市发展还不足以重新填满市中心。
底特律的创意阶层分布在城市西北部郊区的大片楔形区域,从著名的八英里路向外,包括芬代尔、皇家橡树、高端的伯明翰和布卢姆菲尔德镇。底特律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都位于这片郊区地带(见图7.12)。其中两个在伯明翰、两个在布卢姆菲尔德镇、一个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所在的布卢姆菲尔德山、一个在特洛伊、两个在有公共高尔夫球场和底特律动物园的亨廷顿森林,还有两个在格罗斯波因特,包括格罗斯波因特湖滨区和格罗斯波因特公园,在这里各色镀金时代的豪宅林立于湖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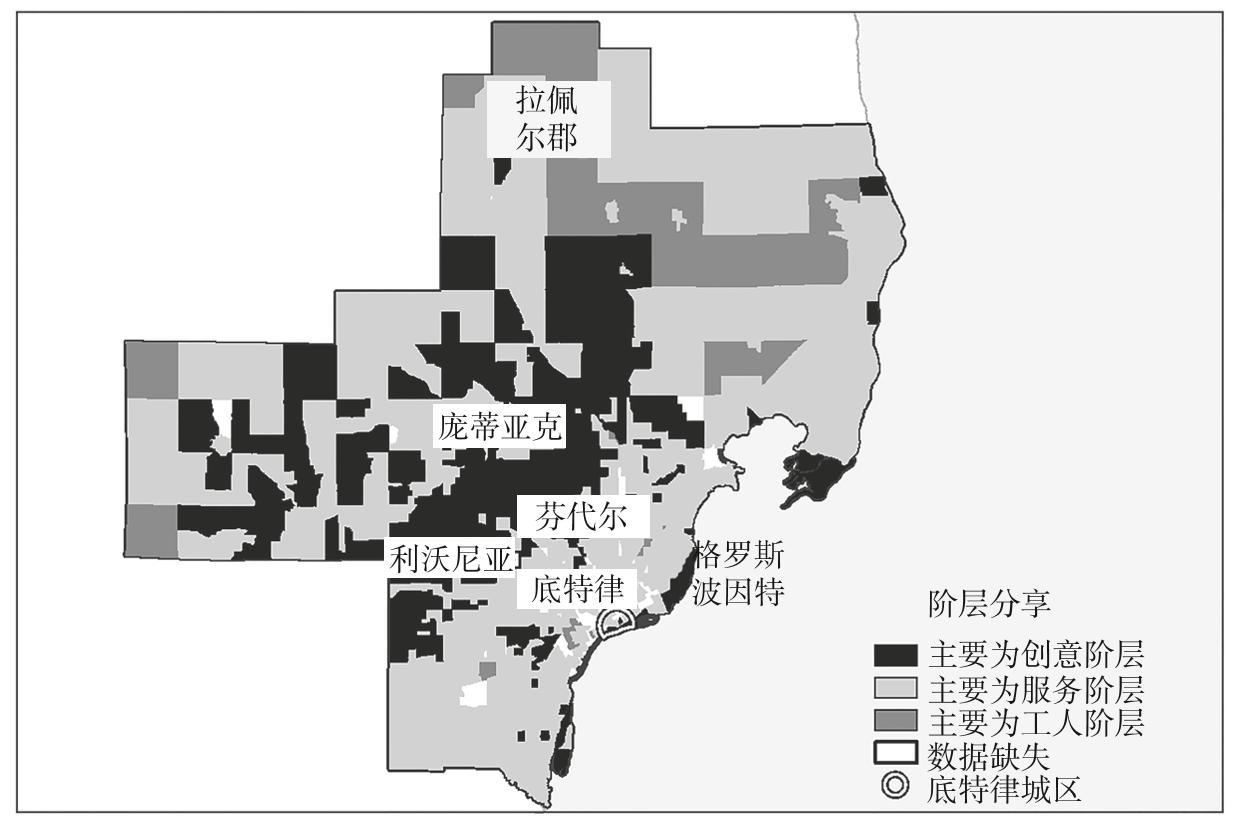
图7.12 底特律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作为受“白人群飞”影响最严重的美国城市之一,底特律地区的阶层分布掩盖并巩固了它长期存在的种族分裂问题。不过它的市中心还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小型创意阶层中心,包括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拉斐特公园社区、库克镇、众多主要艺术文化机构所在的卡斯走廊和韦恩州立大学所在的中城。底特律的市中心获得了大量投资,亿万富翁丹·吉尔伯特更是在它的很多老地标建筑中购下了成百上千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和住宅房产(他曾说自己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摩天大楼促销”中捡便宜)。 [12] 沿着杰弗逊大道向北到格罗斯波因特公园的湖滨狭长地带,还有一个小型创意阶层聚居区。传统富人区帕尔默伍兹也是一个创意阶层聚居地。
服务阶层既在底特律市聚集,也大量分布于广阔的郊区。广阔的弱势贫困地区包围着市中心一小片复兴地区。去工业化和“白人群飞”的打击导致底特律市的人口从1950年开始减少了一大半,到现在市区还有大片废弃区域。 [13] 2009年最近一次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该市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近30%。2013年夏天,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该地区最大的服务阶层社区都聚集在底特律市。令人震惊的是,底特律市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大型蓝领阶层社区都在十分偏远的郊区,包括福特汽车总部的所在地迪尔伯恩、通用的庞蒂亚克车厂和费雪车身制造厂所在地庞蒂亚克、通用的罗慕勒斯发动机制造厂所在地罗慕勒斯,以及靠近弗林特的拉佩尔郡。
另一个“铁锈地带”城市匹兹堡是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探讨后工业化变革的基础案例,我们记录了它从国家一流工业中心到知识中心的转变历程。 [14] 大学城促进了这座城市的重建和复兴。一直以来,创意阶层就大量聚集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附近的老居民区,如桑迪赛德、松鼠山和布里兹角,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大型住宅,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见图7.13)。重返城市浪潮也影响了匹兹堡的部分地区,如市中心保存完好的老仓库区——横排区,及其周边地区。不过匹兹堡地区的创意阶层仍然主要分布于城市北部、南部和东部的郊区地带。服务阶层则在市区中较贫困的地区和郊区外围都有分布。工人阶层社区完全从这个曾经的钢铁之都消失了,全都被迁到了更偏远的郊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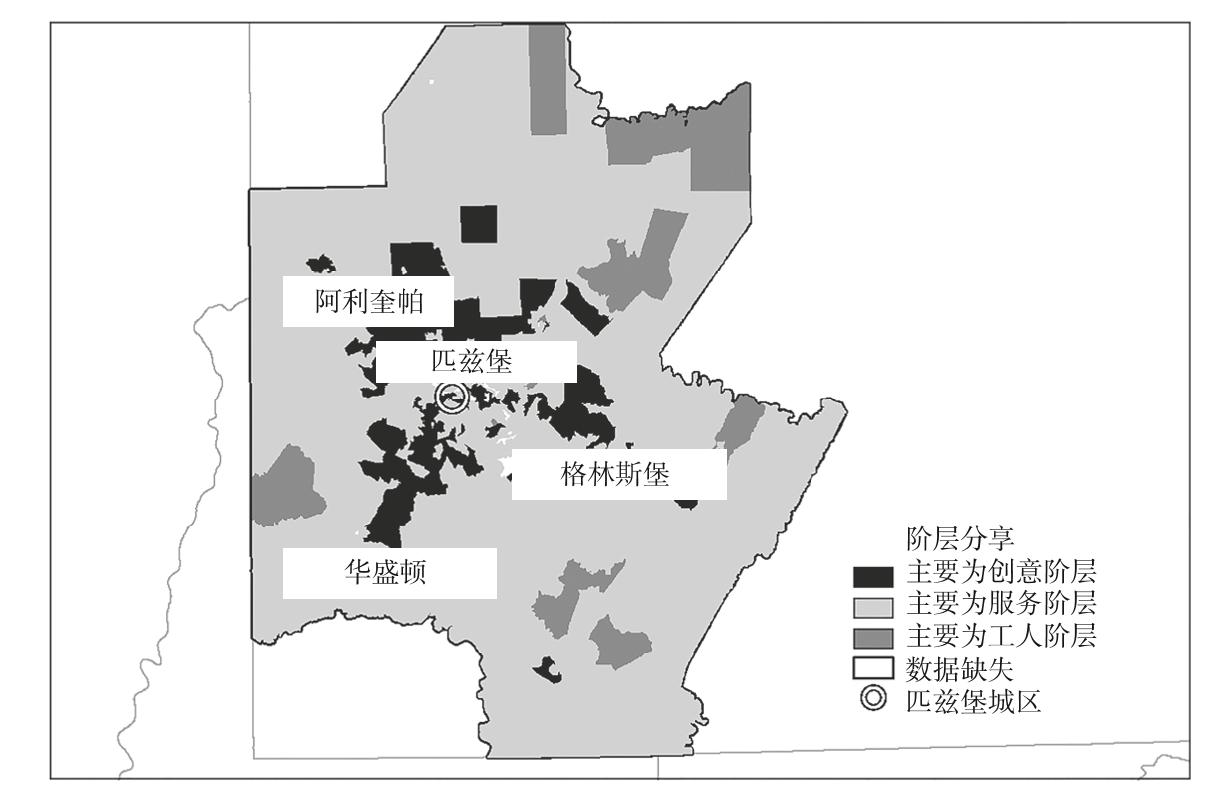
图7.13 匹兹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三种模式中,整片城市地区都被切割为两块,一块被优势创意阶层占据,另一块被其他弱势阶层占据。这种模式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既有与第一种模式类似的创意阶层聚集,但人数更少;又有比第二种模式更明显的重返城市浪潮,但创意阶层又比第一种模式更郊区化。当他们的市中心发生绅士化时,这些地区扩张并混入高端郊区地区,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统一大型创意阶层社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温哥华地区完全被一分为二。创意阶层占据了市中心、西部沿海地段、北部公园周边和环山地区(见图7.14),国内需求和国外资本(主要来自亚洲)的推动让温哥华的市中心高度绅士化。服务阶层几乎全部被挤到城市的东南部,工人阶层社区在温哥华地区则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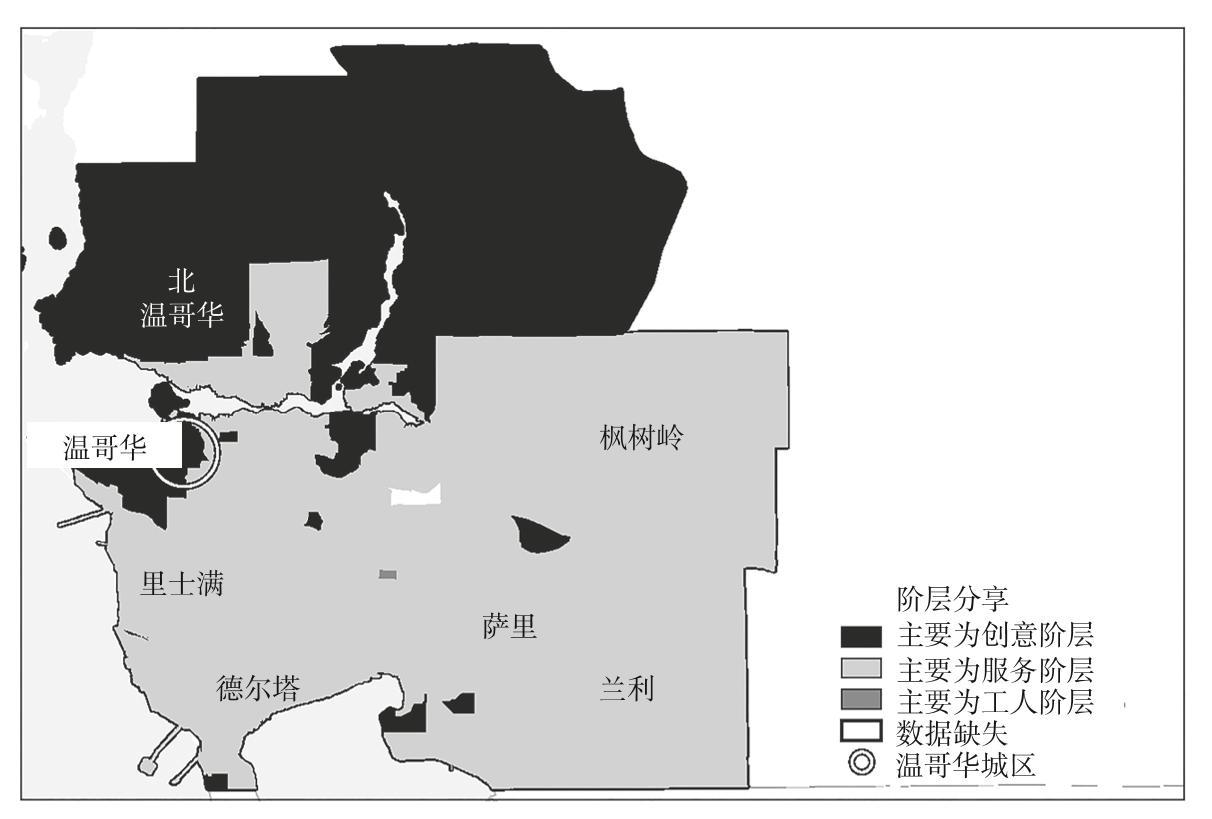
图7.14 温哥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奥斯汀地区则东西分化(见图7.15)。创意阶层聚集在西部从市中心到郊区朗德罗克的大块楔形地区和东南郊区的一片区域。奥斯汀对市中心进行了大力振兴,如大量开发新住宅项目。服务阶层和工人阶级社区分布在市中心东边的贫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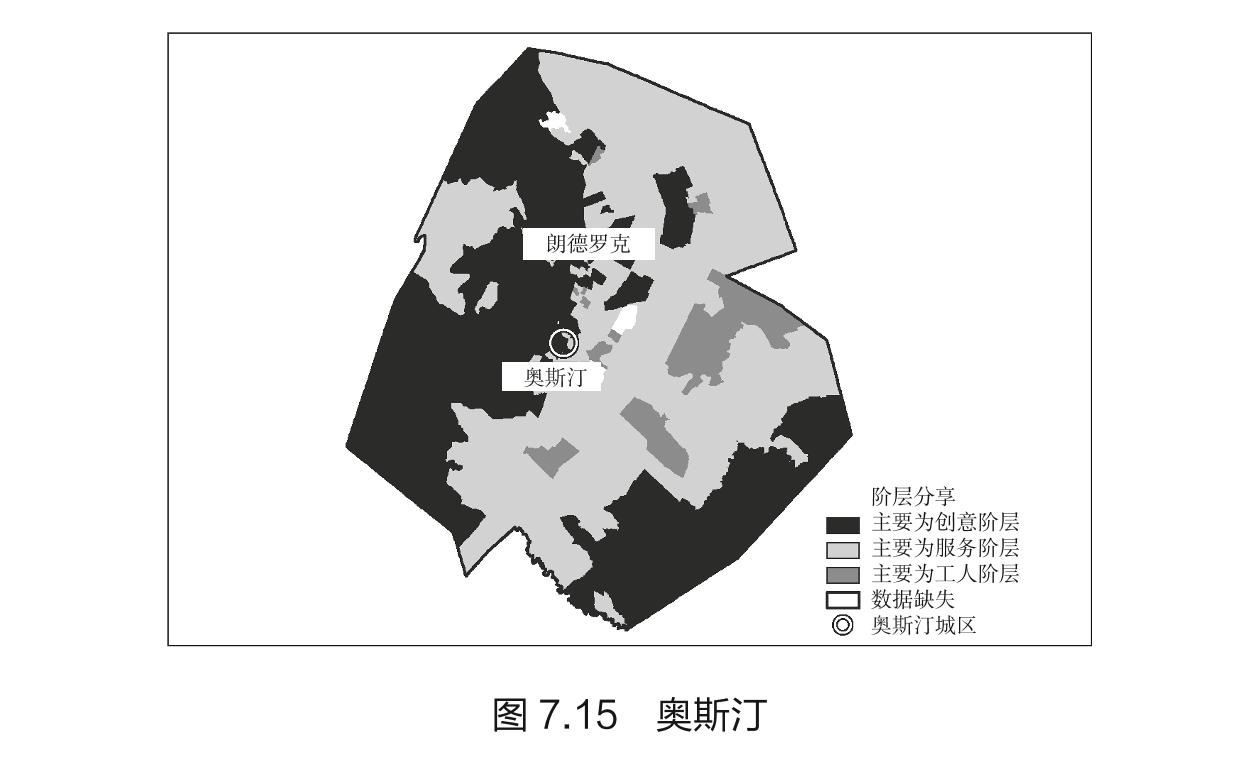
图7.15 奥斯汀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费城地区的创意阶层分别占据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片区域(见图7.16)。在费城市区有两个主要的创意阶层聚居地:其一是在市中心的绅士化地区,包括社会山、里滕豪斯广场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周边;其二是绿树成荫、历史悠久的栗树山和罗克斯伯勒周边地区,这里也是圣约瑟夫大学和费城大学所在地。服务阶层分布在两片主要创意阶层地区之间的带状地区域和更边缘的地带。费城地区的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两个在费城市区,尤其是北边的贫困社区。费城地区只剩下3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分别在东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南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和多佛周边地区,以及东北部的特伦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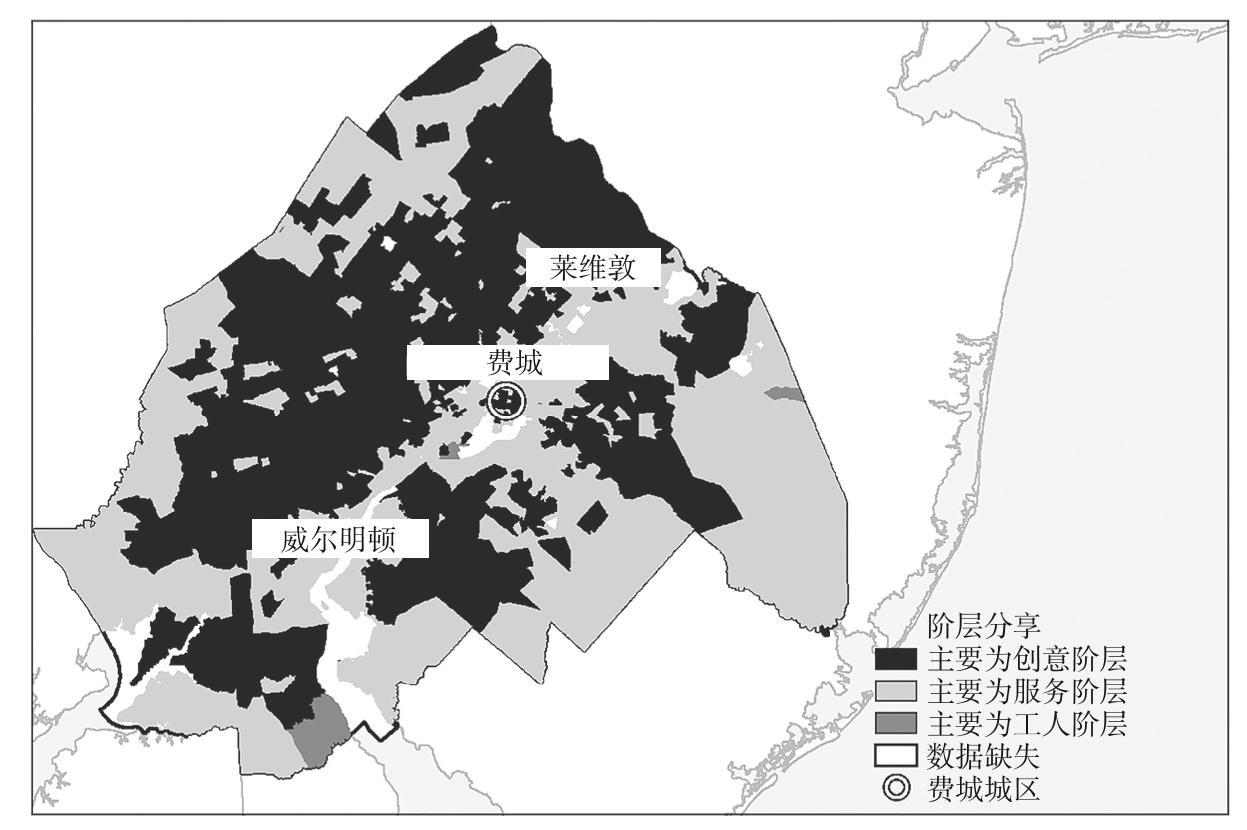
图7.16 费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第四种模式是创意阶层零散分布在市区和郊区的一些独立地区,该模式的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与东北部和中西部那些围绕老工商业中心发展的老城市不同,这两个典型后工业化城市的阶级地理分布主要受高速公路和汽车影响,呈现分散化特征。在这两个城市地区中,优势的创意阶层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复兴的市中心地区也有分布。
洛杉矶的创意阶层沿着风景壮丽的海岸线而居,从北边的马里布一路延伸到南边的尔湾、拉古纳海滩和达纳角,并向东部内陆大范围扩张(见图7.17)。几个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地在好莱坞、贝沙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在的西木区和威尼斯一带、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在的帕萨迪纳,以及东南部尔湾的加州大学周边也各有一片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区。在洛杉矶市中心,艺术家对老式高层建筑进行改造,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型创意阶层社区。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聚集区夹在市中心的创意阶层社区之间,也大量分布在郊区。一大片服务阶层聚居地就位于西边的圣莫尼卡和东边的帕萨迪纳之间,并向南延伸至安纳海姆和圣安娜。另外,洛杉矶的北部和东北角各有一个主要服务阶层聚居区,在市中心和好莱坞之间也有一个服务阶层的聚居区。洛杉矶的工人阶层则聚集在伯班克、南部的老黑人城市康普顿以及长滩的大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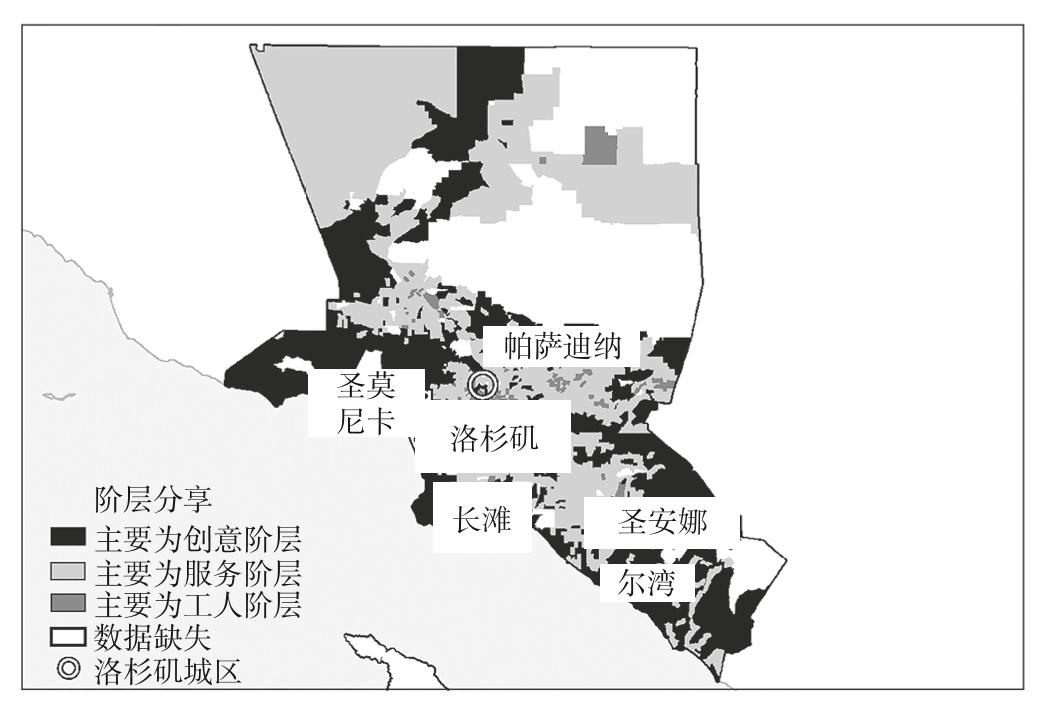
图7.17 洛杉矶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迈阿密地区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岸线沿线(见图7.18),该地区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六个都在这里。另外有三个社区在大学附近,包括科勒尔盖布尔斯的迈阿密大学、博卡拉顿的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和迈阿密西部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五个在迈阿密市区,特别是市中心和沿海地段(旅游胜地南海滩和超级富裕的棕榈滩社区不属于创意阶层社区,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大量购置二套房的非居民房主和退休人士)。该地区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人口都是服务阶层,位居全国前列。服务阶层分布在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包围着创意阶层社区。迈阿密几乎所有居民中超过70%的服务阶层的社区都在内陆地区。迈阿密的阶层地理特征就是沿海超级富豪社区和靠近内陆地区的贫困社区毗邻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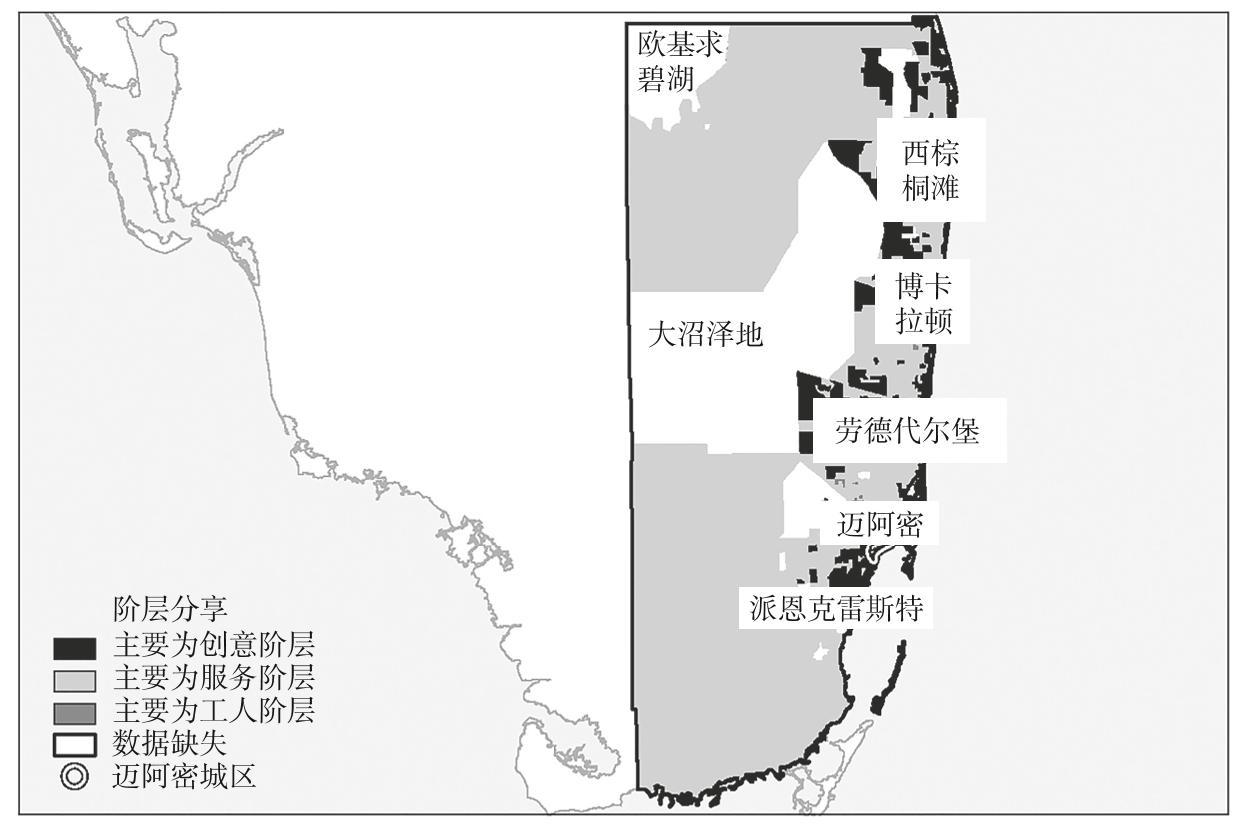
图7.18 迈阿密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以上就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8个城市的拼布城市模式。有的地方的优势创意阶层大量搬回市区,而有的地方的创意阶层则更偏好郊区。在一些地方,不同的阶层各自占据大片独立领地;而在另一些地方,不同阶层的分布更加分散。不过在所有城市地区,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都既分布于市区,也分布于郊区。和我小时候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工人阶层社区了,哪怕是在曾经伟大的工业城市芝加哥、波士顿、匹兹堡或底特律。
这种新阶层地理模式广泛存在,并不仅限于以上我们讨论的城市地区。全美的创意阶层都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并与较贫困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我的团队对全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进行的统计分析,更能反映这种新模式的全貌。我们的结果显示,创意阶层社区越来越集中在彼此相邻的区域,而与其他阶层聚集区分隔开,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以服务阶层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呈负相关关系。这一模式也存在于其他阶层维度中,如收入与学历。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更富裕,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占主体的地区则更贫困。创意阶层为主的地区与平均收入和居民中大学毕业生占比都呈正相关;相反,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的地区与这两个指标呈负相关。在美国,这三个阶层都分布于完全不同且各自独立的地理空间中。 [15]
最后,拼布城市主要受强势创意阶层聚集的主导,创意阶层占据了最具经济价值和最赏心悦目的地区,而其他阶层只能去他们挑剩的地方。这种新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伤害极大。优势群体在占领最好社区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好的经济机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公共设施,这些都强化了他们原有的优势,也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了更多向上流通的机会。更贫困的人群则被挤到犯罪率更高、学校更差、向上流动性更小的社区。简单来说,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穷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
正如我们看到的,经济弱势已经从市区扩展到了郊区。郊区曾是美国梦的支柱,如今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在下一章我会讨论新城市危机中日渐深化的郊区问题。
[1]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Robert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5).
[2] Alan Ehrenhalt, 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New York: Knopf, 2012).
[3] 我们用人口普查区在地图上标注了三个阶层的居住地点,我们在分析中排除了人口小于500人的极小地区。美国城市地区的数据来自201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参见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伦敦的数据涵盖了为低尺度高等级输出区域(Lower Level Super Output Areas, LSOAs),大约等同于美国人口普查区,数据由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加拿大的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在地图上标出了市中心(以市政厅为中心方圆两英里的区域)、主要公共交通路线、大学和知识研究机构以及公园、公共空间、河岸和海岸等自然公共设施,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赘述。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Patrick Adler, “The Patchwork Metropolis: The Morphology of the Divided Post-Industrial Cit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September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2015-MPIWP-006_Patchwork-Metropolis_Florida-Adler.pdf; 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 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divided-city-and-the-shape-of-thenew-metropolis。
[4] Terry Clark, Richard Lloyd, Kenneth Wong, and Pushpam Jain,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4, no. 5 (2002): 493–515; Richard Florida,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 (2002): 743–755; Edward Glaeser, Jed Kolko, and Albert Saiz,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no 1 (2001): 27.
[5] 参见 Robert Owens, “Mapping the C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1920–1934,” American Sociologist 43, no. 3 (September 2012): 264–293;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6] Robert Ezra Park, Ernest W. Burgess,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The C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Burgess also published a seminal study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ee Ernest W. Burge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40, no. 1 (November 1928): 105–115.
[7] Homer Hoyt,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1939; Chauncy Harris and Edward Ullman, “The Nature of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42 (1945): 7–17.
[8] On the flight from destiny, 参见 Edgar Hoover and Raymond Vernon,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 and Jobs With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后来弗农发明了经典的工业地点的产品周期模型,解释了标准制造业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何以使工厂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廉价的郊区绿地和海外。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no. 2 (May 1966): 190–207. On the edge city, see Joel Garreau,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被称作“洛杉矶学派”的城市学家在回顾后工业大都会地区的种种变化后认为,洛杉矶和其他太阳带地区的大都会地区不再是从市中心向外环形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分散的发展模式,有多样化的工业、商业和居民区。参见Michael Dear,“The Los Angeles School of Urban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Urban Geography 24, no. 6 (2003): 493–509。
[01] 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9] J. David Hulchanski,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2005,” Cit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www.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curp/tnrn/Three-CitiesWithin-Toronto-2010-Final.pdf.
[10] Sam Bass Warne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Richard Florida, “Detroit Shows Way to Beat Inner City Blu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9, 2013; Richard Florida, “Don’t Let Bankruptcy Fool You:Detroit’s Not Dead,” CityLab, July 22, 2013, 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3/07/dont-let-bankruptcy-fool-you-detroits-not-dead/6261;Tim Alberta, “Is Dan Gilbert Detroit’s New Superhero?” National Journal,February 27, 2014, www.nationaljournal.com/next-economy/america-360/isdan-gilbert-detroits-new-superhero.
[13]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Richard Florida, “Visions of Pittsburgh’s Future,” Pittsburgh Quarterly(Fall 2013), http://pittsburghquarterly.com/pq-commerce/pq-region/item/82visions-of-pittsburgh-s-future.html.
[15] 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62)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77)负相关。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7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90)高度正相关。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49)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45)负相关,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也与平均收入(-0.56)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78)负相关。
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我两岁、我弟弟罗伯特快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从纽瓦克的出租公寓搬到了北阿灵顿一个工人阶层郊区,我父母花了15000美元买了栋带小后院的科德角式房屋。常听我父亲说,我们的新家所在的社区不久前还是个农场。
就在我们搬家前不久,当时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个全新精装样板房的厨房里举行了会面。这栋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郊区房屋是美苏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被建在了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1959年7月24日,电视台记录了两国领导人的即兴“厨房辩论”。“任何一个钢铁工人都能买得起这栋房子,”尼克松指出,“他们的时薪是3美元,如果申请25年到30年的贷款,这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要100美元。” [1] 赫鲁晓夫反驳道:“只要你出生在苏联,就能有一栋房子。”
会谈的主题随后很快就转向了国际政治和核武器,但是尼克松的发言比房子本身更生动地反映了战后时期的美国梦:一栋带电视、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房子,加上两辆私家车,这是任何一个像我父母那样的工人阶级都能拥有的生活。愿景很美好,现实未必有这么理想。比如我们家的电视机和洗衣机经常出故障,那辆20世纪50年代的雪佛兰的脚踏板都生锈了,时不时就要送去维修。另外,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说,有限的经济机会和种族歧视(比如限制性契约、排他性区域规划、不公平的贷款政策)把他们完全隔绝于郊区之外。
不过我父母还是常常感叹自己能拥有这栋郊区房屋是何等幸运,他们在这里养育子女,也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我在北阿灵顿长大,从一年级开始就步行上学,骑着变速单车到处跑,打棒球和橄榄球,还和我弟弟一起组建过摇滚乐队。最开始我们还会经常回纽瓦克探望亲戚,上音乐课,去繁华的市中心购物。到我青少年时期后,纽瓦克的亲戚逐渐搬走,纽瓦克市中心的很多百货大楼纷纷倒闭,我们回去得也越来越少了。
当时在不远的伍德布里奇和利文斯顿,社区里新开了郊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立交桥附近开始出现工业园区和办公楼。这种变化是全国性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科技工业在波士顿、旧金山、奥斯汀和西雅图的郊区蓬勃发展,很多曾经的郊区“睡城”慢慢变成了成熟的卫星城,人们在郊区生活、工作和购物,不再需要专门跑到大城市中心去。虽然曼哈顿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但我到上高中才第一次去。随着市中心的快速衰退,美国逐渐变成了一个郊区国家。
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富裕、高学历、年轻及无子女的白人群体正在重新搬回市区,而移民、少数族裔和穷人正迁往郊区。与此同时,很多在我父母辈看来只会出现在城市的问题,如贫民窟、贫困、犯罪、毒品、种族矛盾、暴力、结构性失业、流浪汉等,现在也纷纷涌入郊区。
郊区曾是繁荣与希望之地,如今却大规模陷入经济衰退和贫困的泥潭。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方面正在空心化,就像几十年前的城市;另一方面又分化为集中贫困和集中富裕地区,就像今天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意识到郊区正在走下坡路,但我当时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同事、城市设计师大卫·刘易斯告诉我,和未来的郊区复兴项目相比,20世纪的大规模城市复兴很可能就是小菜一碟。事实上,那时很多占地面积巨大、充斥着劣质建筑和仓促建成的基础设施的郊区已经开始衰退了。全国有成百上千的郊区购物广场被荒废;几十年前的城市工厂停工的情景又在无数郊区工厂上演;有些郊区衰落速度极快,被称作“城市贫民窟”的反攻。 [2]
矛盾的是,新城市危机中郊区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越城市问题。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郊区人口更多。郊区人口很难被精确统计,不过对美国居民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人(53%)称自己住在郊区,5个人里面只有1个(21%)称自己住在农村地区,1/4(26%)的人称自己住在市区。 [3] 事实上,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那些最大的城市)中,还有42%的受访人称自己住在郊区。这说明至少在美国人心里,美国还是一个非常郊区化的国家。
很多典型郊区比著名城市的人口更多。比如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郊区梅萨拥有46.5万人口,比亚特兰大(45.6万)、迈阿密(43万)和明尼阿波利斯(40.7万)都多。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远郊贝克尔斯菲尔德拥有36.9万人口,超过了圣路易斯(31.7万)、辛辛那提(29.8万)和匹兹堡(30.5万)。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郊区普莱诺有27.8万人口,超过了布法罗(25.9万)。
优势精英阶层会重返市中心,但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留在了郊区。大学以上学历的单身人口或年轻父母是重返城市的主力军;子女年龄较大的家庭主要从城市向郊区迁移;而老年人和婴儿潮一代中较年轻的群体则继续留在郊区。同时,大批较贫困和学历较低的人群也在迁往郊区,有些人是自愿的,但更多都是迫不得已——他们原来的社区被新城市精英占领了。虽然高科技和知识型工作正在回到城市,但郊区仍是美国最大的就业岗位来源,为美国创造了54%的就业岗位。 [4]
如今的郊区已经不再是《天才小麻烦》、《唐娜·里德秀》或《老爸最知道》里那样的纯白人地区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一开始就直接跳过城市,定居在大城市地区的郊区。在2000—2010年,美国前100大城市地区的郊区人口增长中只有9%来自白人,其中有1/3城市郊区的白人人口甚至减少了。 [5]
当然不是所有郊区都在收缩。现在很多迁往郊区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不比我父母那时差,有些人还比我父母那时富裕多了。虽然有的郊区衰落了,但仍有很多郊区在繁荣发展,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问题。
郊区对耐用品的大量需求曾大大促成了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而在现在这个聚集驱动创新的时代,散漫扩张的郊区则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郊区不动产分流了资本,减少了对更有生产力的知识、科技和人才领域的投资。以前郊区象征着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愿景——所有人都可以向上流动的美国梦,而今天郊区则陷入了新城市危机最深层的矛盾中。
郊区危机之所以如此棘手,部分原因是它的发生太出乎意料了。美国郊区中有超过1/4的贫困或接近贫困人口。事实上,美国大城市地区的郊区比城市的贫困人口更多,郊区贫困的发展速度也更快。从2000—2013年,美国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加了29%,而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加了66%。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达到了1700万,城市贫困人口为1350万。 [6]
美国郊区贫困是全国性问题,并在逐步恶化。2000年,纽约地区有29%的贫困人口住在郊区;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5%。同期,贫困人口分布在郊区的比例在大费城地区从44%上升到50%,在大达拉斯地区从41%上升到48%,在大西雅图地区从61%上升到69%,在大旧金山地区从52%上升到59%,在大圣路易斯地区从68%上升到77%,在大华盛顿地区从61%上升到70%,在大亚特兰大地区从76%上升到88%。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伦敦郊区的贫困人口数量(122万)高于伦敦市(102万)。 [7]
从2000—2012年,郊区的集中贫困社区(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40%)居民数量上升了139%,增长速度是城市的三倍。同期,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20%的贫困社区的居民数量在郊区上升了105%,在城市仅上升了21%。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占比最高的地区不是超级城市纽约、科技中心旧金山,甚至也不是经济遭受重创的“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而是曾经郊区梦的典范——位于加州内陆帝国中心的圣贝纳迪诺。 [8]
郊区的新增贫困人口中,有的人是因为无力负担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而被迫迁往郊区,但也有很多人是曾经体面的郊区中产阶级,他们要么就是丢了工作,要么就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房价暴跌。
与此同时,几十年前可能会选择住在郊区的一部分优势群体现在重新搬回城市了。约50年前,大量美国人离开了高密度的城市地区,而现在美国人则开始离开散漫扩张的低密度郊区。郊区人口增速逐渐放缓,有的甚至跟不上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这标志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城市向郊区人口迁移浪潮开始退去。 [9]
城市和郊区房价的相反变动反映了逃离郊区的趋势。过去很多年中,郊区房价都一直高于市中心房价,而到2015年底,城市平均房价均值比郊区平均房价高了两个百分点,前者是269036美元,而后者是263987美元。但这低估了城市和郊区房价的实际差异,因为郊区房屋面积普遍大于城市房屋。如果按照每平方米价格来算,郊区和城市房价的差异就更大了。
这一趋势在重返城市浪潮更明显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十分显著。在大波士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的房价均值都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而到2015年,城市的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英尺400美元,而郊区则为每平方英尺250美元。在华盛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房价也均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300美元和225美元。在旧金山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平均房价都约为每平方英尺150美元,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700美元和不到500美元。 [10]
以前的郊区一派宁静祥和,现在则面临犯罪率攀升、经济疲弱和人口流失的问题。《绝命毒师》让城市街角作为毒贩交易中心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电视剧《火线》带火了郊区的安非他命兴奋剂。近年来阿片药物的流行就来自郊区。另外,从1990—2008年,虽然美国整体暴力犯罪率都在下降,但美国主要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下降速度比郊区快了3倍。2001—2010年,谋杀案在郊区上升了16.9%,而在城市下降了16.7%。 [11] 从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很多大规模枪击案都发生在郊区。
郊区的政府和警察还没有适应这些新形势。从2015年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案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就能看出来。这个圣路易斯市的郊区有超过2/3(67%)的黑人人口,而全镇54个警察中只有4名是黑人。弗格森镇不算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还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失败的机场扩张项目让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搬迁,以及银行住房贷款针对黑人的“红线政策”。但它衰落的原因也包括更广泛的人口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美国郊区。弗格森的失业率从2000年到2014年几乎增加了两倍——从不到5%上升到超过13%。而同期有工作的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则下降了1/4。到2015年,有1/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12] 弗格森不仅仅是警察滥用权力的典型案例,还象征着越来越多美国郊区的衰落。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不仅困扰郊区居民,还影响了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郊区的散漫扩张不仅能源利用低效且浪费,还会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并削弱生产力。
郊区房产曾是美国梦的基石,如今则成了美国人向上经济流动的阻碍。俗话“一直往外开,直到住得起”反映了在越远的郊区,房价越便宜。然而,住得远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一般来说,人们的住房支出应占收入的1/3左右,住房和交通支出总和不超过收入的45%。几辆车的购买费用再加上保险、维修和加油的费用并不便宜,而住在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地方则意味着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大幅削减交通支出。因此,住在市中心附近或公共交通沿线的公寓,可能比住在依赖汽车出行的郊区别墅更划算。
如今的郊区不仅不能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还阻碍人们实现向上的经济流动。大面积和低密度城市地区的经济流动性显著低于人口密集的城市。郊区的低收入工人比城市工人离工作中心更远,更难找到工作,上班也更不方便。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时间显著影响了他们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通勤时间越长,经济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城市的贫困社区可能会形成集中和持续的贫困循环,郊区的贫困社区也有自己的问题:社区居民被隔离于工作岗位、经济机会和用来削弱贫困影响的社会服务。虽然郊区也有社会服务,但因为信息更封闭、更不方便获得,穷人往往很难享受到。 [13]
郊区散漫扩张的整体经济成本十分高昂。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或本地资源在郊区的运输成本是城市的2.5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加州富裕城市马里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630人)的居民平均能源消耗量是贝尔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4000人)的10倍有余。根据201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每年约6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如低效率土地利用和汽车依赖,另外还有4000亿美元间接损失,如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两者相加就是每年10000亿美元。 [14] 长距离通勤带来了额外的成本。美国工人平均每天上下班的总通勤时间为52分钟,一年通勤时间就超过了9个整天,而每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人则每年要在上下班路上浪费超过约1个月的时间(31.3天)。美国有1.39亿通勤人口,每年一共要在路上浪费300亿个小时。如果能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360万美国人把单程通勤时间压缩到30分钟的平均水平,并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工作,就相当于每年给美国增加18亿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者90万份全职工作。 [15]
如果把间接损失也考虑在内,散漫扩张的广泛社会成本更高。住在远郊区、长通勤时间的居民更容易出现肥胖、糖尿病、焦虑、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们的自杀率和车祸死亡率也更高。以上所有风险导致郊区居民的平均寿命减少了3年。根据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的调查,人们在各项日常活动的偏好排名中,通勤排在最后,低于工作、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16] 当我们想到通勤者时,可能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手提公文包、西装革履并和妻子吻别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个穿着休闲、开跑车的科技工作者。但实际上,通勤的负担主要落在了穷人和更弱势群体的身上。知识工人和专业人士最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方便的公共交通沿线,如果他们住在依赖汽车的郊区,也能开私家车安全舒适地上下班。但是,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更可能住在远离公共交通的地方,很多人也买不起车。他们的郊区通勤主要靠多次换乘公交车和火车,往往还要在人行道不足的地方长时间步行。
散漫扩张的郊区不仅影响经济流动性、效率和生产力,还在逐步丧失工作制造引擎的地位。虽然郊区创造工作的能力仍比城市强,但差距在逐渐缩小。2007—2015年,在美国3000多个县郡中,纽约的金斯县(即布鲁克林)的就业岗位增长率最高。2007—2011年,在美国41个大城市地区中,有一半(21个)地区的市中心区域(距市中心商业地带方圆3英里之内)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它的郊区,其中包括夏洛特、俄克拉何马、密尔沃基、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旧金山和奥斯汀等。虽然整体郊区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市中心,但郊区新增就业主要是低薪、低技能要求、更容易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的岗位,而市中心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知识型和专业岗位。市中心的平均工资比高密度和更城市化的郊区高20%,比低密度郊区高37%。 [17]
虽然现在更多穷人住在郊区而非城市,很多郊区的经济前景也十分堪忧,但还是有很多富人留在郊区。尽管有富人重返城市的浪潮,但不管从收入水平还是房产价格来看,美国最富裕的地区几乎都在郊区。
美国最富裕的10个地区中有9个在郊区(见表8.1)。这一精英群体的最低家庭年收入是54万美元,超过“前1%”群体收入门槛的两倍有余。 [18] 排名第一的是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名副其实的“金三角”,平均家庭年收入超过60万美元。其他地区包括华盛顿、迈阿密和洛杉矶的精英郊区飞地,只有芝加哥的东湖湖岸是城市地区。最富裕的城市地区比最富裕的郊区地区更加多元化,前者的住宅类型和收入阶层更多样,租户也更多。
表8.1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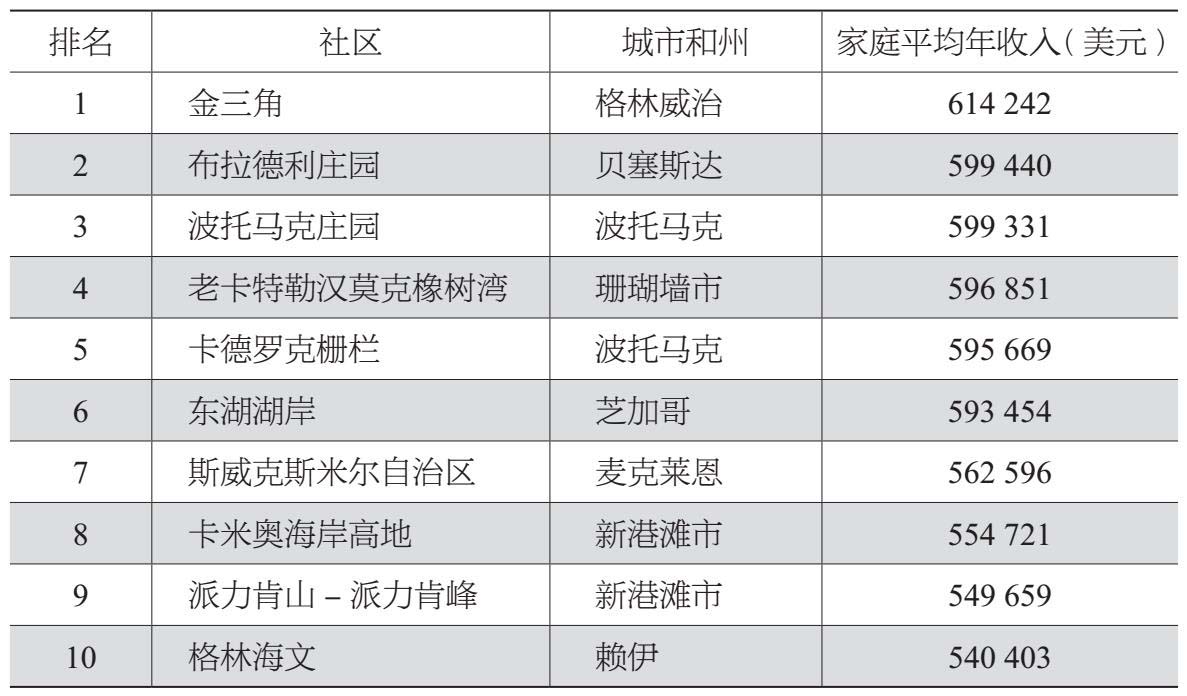
资料来源:史蒂芬·希格利,希格利1000数据,Higle 1000.com, 2014年2月,Http://higley 1000.com/archives/638。
房地产价格反映了同样的事实(见表8.2)。美国最贵的10个邮政编码区中有9个在郊区,唯一的例外是纽约的翠贝卡与苏荷区。 [19] 这些郊区地区中有8个都在加州,包括精英硅谷郊区阿瑟顿、洛斯阿图斯和帕洛阿托,以及比弗利山庄、圣莫尼卡、圣迭戈的兰乔圣菲和圣塔芭芭拉的蒙特西托等。另外还有在迈阿密海滩对岸只能乘船或乘游轮到达的高级飞地费希尔岛。
表8.2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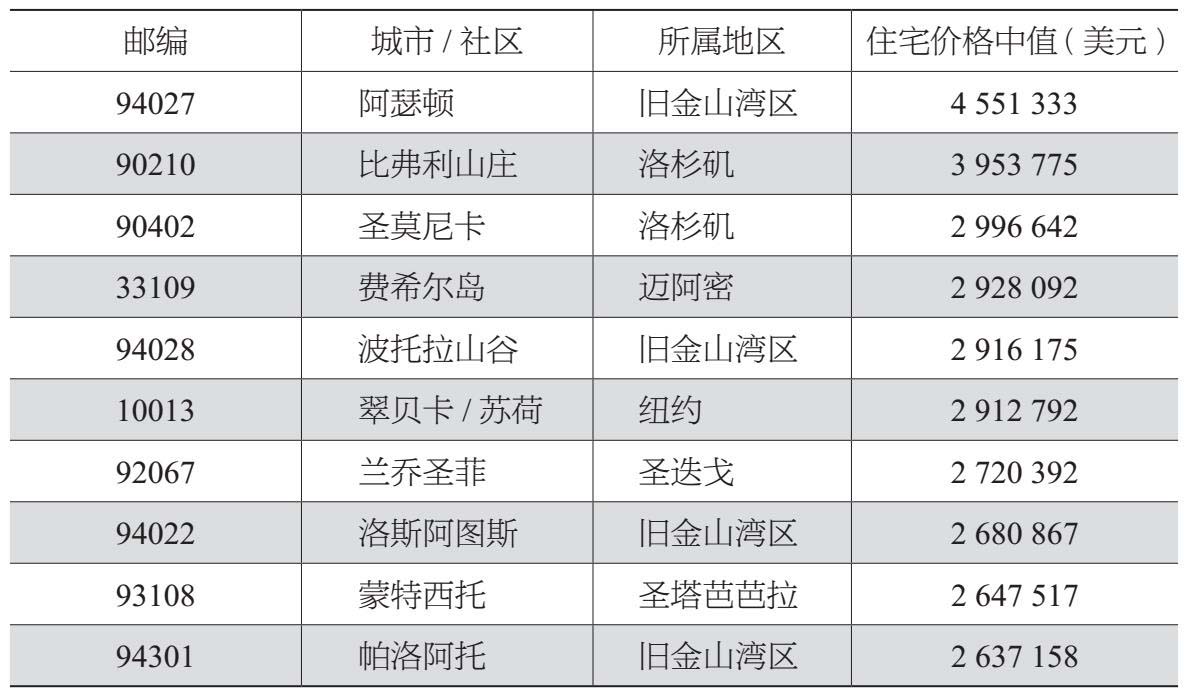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马丁繁荣研究所的分析,以及Zillow住房价值指数(2014)。
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只看最富裕的地区,城市社区和郊区社区之间的传统差异几乎消失了。几年前我在一次晚宴中目睹了两对夫妻关于城市和郊区哪里更宜居的争论,他们都来自大纽约地区,其中一对住在郊区的费尔菲尔德,另一对住在曼哈顿。我从争论中发现,尽管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但除了个别明显差异,如一对夫妻住公寓而另一对夫妻住独栋别墅,他们的生活方式竟然十分相似。他们在相似的地方购物,在相似的餐厅吃饭,穿相似的衣服,享受相似的公共设施,甚至他们的孩子上的学校都极为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因为住在城市或郊区而改变,而是由社会经济阶层和社区主要阶层构成决定的。
和城市一样,有的郊区富,有的郊区穷;有的郊区快速发展,有的郊区正在衰落。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高密度的城市地区和边远的郊区外围。房地产经济学家杰德·柯尔克的研究表明,在最边远的郊区地带(最“郊区”的地区)和最密集的城市地区,人口增速最快。 [20] 在边远地区广阔的处女地上建房子便宜得多,也没有什么比从零开始的发展速度更快了。而高密度城市地区利用其便利性和高生产力不断吸引着人口和工作。同时,郊区的中心正被掏空并遭到了经济排挤,经济发展绕过了位于市中心和新开发边远郊区之间的老郊区地区。
老郊区的经济停滞和衰落对今天的美国影响深远。除了影响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和国家经济之外,它们还造成了政治地震。 [21]
郊区贫困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位起了关键作用,他利用了郊区贫困工人阶级一触即发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根据我的调查,特朗普主要靠白人、蓝领、低学历和老社区居民赢得了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特朗普在初选中获得的选票集中在白人、蓝领“老经济”工作者、高中学历以下人口和住低端移动屋人口更多的郡。 [22]
相互重叠的阶层和地理分化让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在阶层上,他的支持者主要是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的白人、低学历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地理上,他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白人和低学历人群占比大、经济焦虑程度高、工厂和服务业工作聚集的地区。在农村,特朗普获得了61%的选票,而希拉里只有33%;在人口少于25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7%和38%的选票;在人口为25万~50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2%和34%的选票。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多于希拉里,前者为260个,后者为120个。但是希拉里获得的城市地区选票数量更多,她赢得了51%的城市选票,特朗普只有44%。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平均人口仅为42万,而支持希拉里的则为140万。 [23]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局面。我们都对选举中的蓝州和红州耳熟能详 [24] ,但真正将民主党和共和党地区分开的不是州界,而是人口密度。在过去几任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总是在面积大、人口多、更城市化的地区获胜,而共和党候选人则占领了低密度的郊区和面积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民主党赢得了大城市地区的支持,而共和党则在中小型城市获胜。 [25] 人口密度在总统选举中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默认分界指标,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800人的地区一般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高于800人则是支持民主党的蓝州。 [26]
然而,两党相争的焦点在于受到经济压迫的“中间地带”。它们位于民主党占领的城市中心和共和党占领的远郊地区之间,是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重要的“临界点地区”。政治研究家杰弗里·塞勒斯认为,红州中的贫困郊区会变蓝,而蓝州中的贫困郊区则会变红,他写道:“红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最容易在政治倾向上与支持共和党的其他地区发生分歧,而蓝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响应共和党的号召。”换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地区更不稳定,更可能持相反立场,也更倾向于为改变现状投票。2012年,罗姆尼争取到了2%的动摇地区的支持,再往前的2008年,奥巴马争取到了更多动摇地区。 [27] 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在经济贫困郊区的显著优势,尤其是“铁锈地带”地区,帮助他攻下了一直以来都是蓝州阵营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支持英国脱欧和罗布·福特的也是类似地区,这三件事都明确警示着日益严峻的郊区危机所造成的政治不满。
归根结底,郊区危机反映了很长一段时间廉价经济发展的终结。一直以来,相比在成熟城市修建新地铁、隧道和高楼,在处女地上修路、盖楼或建设其他基础设施更能以极低的成本帮助大众实现美国梦。在20世纪50—90年代,郊区化都是美国工业化经济的完美补充。郊区发展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经济发展期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备战工作或凯恩斯刺激政策。郊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对洗衣机、烘干机、电视机、沙发、地毯、汽车等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从而进一步拉动需求。 [28] 当时郊区的散漫扩张是廉价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现在这一发展模式正走向尾声。
现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聚集而非分散。虽然还有很多人喜欢住在郊区,但是郊区发展已经跟不上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大量宝贵的生产资本和国家财富都被浪费在房屋、公路和散漫扩张的郊区,而没有被投资于知识、科技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而后者才是优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郊区还没消亡,但它们已不再是美国梦的典范,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新城市危机中的郊区问题和城市问题有相似的解决方案:继续发展城市化,并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想要解决郊区危机并恢复郊区经济活力,就得提高郊区的人口密度,让郊区更节能环保,更多功能化,并使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通更便利。不过在我们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有必要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维度,它发生在全球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大都会地区。
[1] Dis, “The Nixon-Khrushchev ‘Kitchen Debate,’” Everything2, April 26, 2000,http://everything2.com/title/The+Nixon-Khrushchev+%2522Kitchen+Deba te%2522.
[2] On dead malls, 参见 Nelson D. Schwartz, “The Economics (and Nostalgia) of Dead Mal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5, www.nytimes.com/2015/01/04/business/the-economics-and-nostalgia-of-dead-malls.html. The term slumburbia is from Timothy Egan, “Slumburbi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10,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0/02/10/slumburbia。
[3] Jed Kolko, “How Suburban Are Big American Cities?,” FiveThirtyEight,May 2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how-suburban-are-bigamerican-cities.
[4] Jed Kolko, “Urban Revival? Not for Most Americans,” JedKolko.com,March 30,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3/30/urban-revival-notfor-most-americans; Jed Kolko, “City Limits: How Real Is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JedKolko.com, January 29,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1/19/city-limits-how-real-is-the-urban-jobs-comeback. See also Karyn Lacy, “The New Sociology of Suburbs: A Research Agenda for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 (July 2016): 369–384, www.annualreviews.org/doi/full/10.1146/annurevsoc-071312-145657.
[5] Alan Berube, William H. Frey, Alec Friedhoff, Emily Garr, Emilia Istrate,Elizabeth Kneebone, Robert Puentes, Adie Tomer, and Howard Wial, “Stat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010/05/09-metro-america; William H. Frey, “The End of Suburban White Flight,”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3, 2015, www.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5/07/23-suburban-white-flight frey.
[6] Elizabeth Kneebone and Alan Berube, Confronting Suburban Pover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7] Mary O’Hara, “Alan Berube: We Are Moving Poverty to the Suburbs,” The Guardian, May 6, 2015, 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5/may/06/alanberube-moving-poverty-to-suburbs.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Richard Florida, “The Living-in-the-Basement Generation,”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December 2013), www.washingtonmonthly.com/magazine/november_december_2013/features/the_livinginthebasement_genera047358.php;Kristen Lewis and Sarah Burd-Sharps, “Halve the Gap by 2030: Youth Disconnection in America’s C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2013, http://ssrc-static.s3.amazonaws.com/moa/MOA-Halve-the-GapALL-10.25.13.pdf.
[9] William H. Frey, “Demographic Reversal: Cities Thrive, Suburbs Sputter,”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9, 2012, 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6/29-cities-suburbs-frey; William H. Frey, “Will This Be the Decade of Big City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3,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5/23-decade-of-big-city-growth-frey.
[10] Cody Fuller, “Rockin’ the Suburbs: Home Values in Urban, Suburban, and Rural Areas,” Zillow Research, January 16, 2016, www.zillow.com/research/urban-suburban-rural-values-rents-11714.
[11] Elizabeth Kneebone and Steven Raphael, “City and Suburban Crime Trends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Cameron McWhirter and Gary Fields, “Crime Migrates to Suburbs,”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12,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300404578206873179427496.
[12] 弗格森的数据来自 Elizabeth Kneebone, “Ferguson, MO, Emblematic of Growing Suburban Pover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15, 2014, www.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4/08/15-ferguson-suburban-poverty; James Russell, “Ferguson and Failing Suburbs,” Jamessrussell.net, August 17,2015, http://jamessrussell.net/ferguson-and-failing-suburbs; Stephen Bronars,“Half of Ferguson’s Young African-American Men Are Missing,” Forbes,March 18, 2015, www.forbes.com/sites/modeledbehavior/2015/03/18/halfof-fergusons-young-african-american-men-are-missing。
[13] 关于通勤时间和经济流动性的关系,参见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ting time and economic mobility, 也可参见 Reid Ewing, Shima Hamidi,James B. Grace, and Yehua Dennis Wei, “Does Urban Sprawl Hold Down Upward Mobil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8 (April 2016): 80–88。
[14] 关于向郊区运输本地服务,参见Arthur Nelson as cited in Leigh Gallagher,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 (New York:Portfolio Penguin, 2013). 有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参见Laura Bliss, “L.A.’s New ‘Energy Atlas’ Maps: Who Sucks the Most Off the Grid,” CityLab, October 6,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10/lasnew-energy-atlas-maps-who-sucks-the-most-off-the-grid/409135. 当然,贝尔市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这里的居民更少地使用空调和电脑等。关于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总成本,参见Todd Litman,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ies That Unintentionally Encourage and Subsidize Urban Sprawl,”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or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 for the New Climate Economy, 2015, http://static.newclimateeconomy.report/wpcontent/uploads/2015/03/public-policies-encourage-sprawl-nce-report.pdf。
[15] Christopher Ingraham, “The Astonishing Human Potential Wasted on Commute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16, www.washingtonpost. com/news/wonk/wp/2016/02/25/how-much-of-your-life-youre-wasting-onyour-commute.
[16] 关于散漫扩张给居民带来的健康成本,参见Reid Ewing, Gail Meakins,Shima Hamidi, and Arthur C. Nel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rawl and Physical Activity, Obesity, and Morbidity: Update and Refinement,”Health and Place 26 (March 2014): 118–126; Reid Ewing and Shima Hamidi, “Measuring Sprawl, 2014,” Smart Growth America, April 2014,www.smartgrowthamerica.org/documents/measuring-sprawl-2014.pdf; Jane E. Brody, “Commuting’s Hidden Co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3,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3/10/28/commutings-hidden-cost.。关于通勤为什么是人们最不喜欢的的日常活动,参见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o. 1 (Winter 2006): 3–24。
[17] 关于布鲁克林区,参见 Justin Fox, “Want a Job? Go to Brooklyn,” Bloomberg View, January 21, 2016, 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6-01-21/want-ajob-go-to-brooklyn。关于2007年到2011年间市中心附近区域的就业增长,参见Joseph Cortright, Surging City Center Job Growth (Portland, OR: City Observatory,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Surging-City-Center-Jobs.pdf. 2007年到2011年,市中心的年就业增长率为0.5%,而外围郊区地区仅为0.1%,参见Jed Kolko,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Continued: Follow the Money,” JedKolko.com, January 20,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1/20/the-urban-jobs-comeback-continuedfollow-the-money。对于大型都会地区(人口超过100万且贡献了全国就业岗位的绝大多数)来说,郊区提供了54%的就业岗位,其中有38%位于临近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较高的郊区地区,16%位于更偏远、人口分布更稀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参见Kolko, “City Limits.”。
[18] 基于地理学家史蒂芬·希格利对美国最富有的一千个社区的排名,这个排名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平均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The cutoffis based on geographer Stephen Higley’s rankings of America’s 1,000 richest neighborhoods。The list is based on US Census data on contiguous block groups with mean household incomes of $200,000 or more. Stephen Higley,“The Higley 1000,” Higley1000.com, February 17, 2014, http://higley1000.com/archives/638.
[19] 这些数据来自 Zillow的研究网站www.zillow.com/research/data。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的,这些数据不包括如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这些数据保密州。
[20] Jed Kolko, “No, Suburbs Aren’t All the Same; The Suburbiest Ones Are Growing Fastest,” CityLab, February 5,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2/no-suburbs-arent-all-the-same-the-suburbiest-ones-aregrowing-fastest/385183.
[21] Richard Florida, “Welcome to Blueburbia and Other Landmarks on America’s New Map,” Politico (November 2013),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3/11/welcome-to-blueburbia-and-other-landmarkson-americas-new-map-98957.html; Richard Florida, “The Suburbs Are the New Swing States,” CityLab, November 29, 2013,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3/11/suburbs-are-new-swing-states/7706.
[22]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the Republican Primaries,” CityLab,April 12, 2016,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6/04/the-geographyof-the-republican-primaries/477693; Neil Irwin and Josh Katz, “The Geography of Trumpism,”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3/13/upshot/the-geography-of-trumpism.html.
[23] 关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阶层分布,参见Andrew Flowers, “Where Trump Got His Edge,” FiveThirtyEight, November 11,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here-trump-got-his-edge; Jon Huang, Samuel Jacoby, K. K. Rebecca Lai, and Michael Strickland, “Election 2016: Exit Poll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16, 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polls.html。关于地理分布,参见Jed Kolko, “The Geography of the 2016 Vote,” jedkolko.com, November 11,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11/11/the-geography-of-the-2016-vote; and Jed Kolko, “Trump Support Was Stronger Where the Economy Is Weaker,” FiveThirtyEight,November 10,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rump-was-strongerwhere-the-economy-is-weaker。
[24] Andrew Gelman,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5] Dave Troy, “The Real Republican Adversary? Population Density,” Davetroy.com, November 19, 2012, http://davetroy.com/posts/the-real-republicanadversary-population-density. 同样参见 Richard Florida and Sara Johnson,“What Republicans Are Really Up Against: Population Density,” CityLab,November 26, 2012,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2/11/what-republicansare-really-against-population-density/3953.
[26] 我对州级选举的研究显示希拉里得票占比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密度(0.7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63)、工资(0.82)、大学毕业生占比(0.77)和创意阶层(0.72)。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则与这些因素负相关:密度(–0.6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54)、工资(–0.81)和大学毕业生占比(–0.81)。参见Richard Florida, “It’s Still About Geography and Class,” CityLab, November 17, 2016,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6/11/americas-great-divide-of-class-and-geography/507908/。在市级层面,密度和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得票占比的相关度从2000年的0.61上升到了2016年的0.75。参见Kolko, “Geography of the 2016 Election.”。
[27] Jefferey Sellers, “Place,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y of U.S.Metropolitan Areas,” in Jefferey Sellers, Daniel Kübler, Alan Walks, and Melanie Walter-Rog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Metropolis: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Electoral Behaviour in Eleven Countries (Colchester, UK: ECPR Press, 2013), 37–85. Sellers就他称之为美国政治的“都市化”问题整理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库,包含了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底特律、弗雷斯诺、卡拉马祖、洛杉矶、纽约、费城、西雅图、锡拉丘兹和威奇托的投票数据。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参见Emily Badger,Quoctrung Bui, and Adam Pearce, “This Election Highlighted a Growing Urban-Rural Spli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16, www.nytimes.com/2016/11/12/upshot/this-election-highlighted-a-growing-rural-urbansplit.html; Lazaro Gamio and Dan Keating, “How Trump Redrew the Electoral Map,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2016-election/electionresults-from-coast-to-coast。
[28] Eva Jacobs and Stephanie Shipp, “How Family Spending Has Changed in the U.S.,” Monthly Labor Review (March 1990): 20–27.
2014年5月,我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的“可持续城市化”主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其他演讲嘉宾包括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和现任负责城市与人类居住问题的联合国人居署署长华安·克洛斯,以及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伊戈达的竞选承诺是解决城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提供更多的廉价住房。听众席中有联合国负责城市事务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的各组织机构负责人,还有其他顶尖的城市学家。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参加了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来自16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城市学家、领导人和城市规划师出席了会议。会议上通过的《麦德林宣言》指出,城市是我们应对威胁地球的严峻挑战的关键。 [1] 从麦德林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围绕论坛上讨论的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城市是我们面临的众多重大挑战的核心,如气候变化、贫困、就业、公共健康、可持续能源和包容性发展。”我在联合国会议发言时说道,“城市化有巨大潜力,如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经济机会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我们无法单凭城市化本身实现这些目标。应该把城市和可持续城市化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议程。”
那次演讲时,本书的主题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明朗。我开始意识到全球城市与城市化危机是新城市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严重的城市问题与郊区问题。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浪潮,全球城市新增人口将达到70亿~80亿,超过目前全球人口总数,并且这些新增人口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21世纪后半叶,人类活动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中有超过60%还尚未建成,未来投入建设新城市以及重建旧城市的资金将以万亿计。
问题是,这波铺天盖地的城市化浪潮将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像城市乐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发展、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像悲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更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和环境问题? [2] 这一次,正反两派同样都看到了问题的部分关键。
历史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城市化还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跃升为中产阶级。但现在,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很多城市却碰到了棘手的贫困问题。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成百上千万涌入新兴城市的人来说,经济机会远远不够。超过8.4亿人(约全球1/10的人口)被困在了快速城市化地区的贫民窟中。 [3] 问题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全球生存状况堪忧的贫民窟居民人口总数约等于美国和欧盟的人口之和。相较于美日欧等最发达国家地区与最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消失的中层”问题,美国的内部分化就是小巫见大巫,这就是新城市危机的全球问题。
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世界发达经济体城市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城市化的好处,我们的城市化实现于多年以前。现在,正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完成了一波城市化浪潮,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它让全国超过8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还有两波城市化浪潮在等着我们,其中一波是正加速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化——到2025年,中国将会有超过2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另一波即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 [4]
今天大概有一半的世界人口(约35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仅仅在200年前,城市地区人口占比还只有3%。这一数字在工业化发展100年后的1900年上升至15%,到1950年又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人数约为10亿。在未来一到两个世纪内,世界城市人口将增长近两倍,达到近100亿,占全球110亿~120亿总人口的85%。其中约86亿城市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很多城市还尚未建成),只有12亿左右的人口将生活在发达国家城市地区。 [5]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看之前的情况。在180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北京;1900年,这样的城市有12个;195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倍,达到83个;2005年,这一数字爆炸性地增长到400;今天,全世界有超过5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1950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都市——纽约和东京;今天这样的城市有28个;到2030年将达到约40个。一个合理推测是,到2150年,全世界可能会出现10个人口在5000万~1亿的特大都市,届时,印度的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的达卡的人口将达到两亿,超过现在全世界除了前五大国家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 [6]
财富和生产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产生了分化。有个生动的指标反映了这一差异: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经典产品iPhone(苹果手机)等于普通城市工人时薪的多少倍。 [7] 在2015年的纽约市,一个普通城市工人工作24个小时就能购买一台内存16G的iPhone 6;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孟买需要工作350个小时,在雅加达为460个小时,而在基辅则需要超过600个小时。
人均经济产出能更系统性地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差距。不幸的是,常用来比较各国经济状况、薪水、收入和生产力差异的统计数据在城市层面往往很难获取。虽然很多国家也统计城市地区的数据,但各国对城市地区的定义和获取经济数据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对比不同国家的城市数据基本没有意义,即便是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的城市数据。而很多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则根本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我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是想找到成功城市化的驱动力,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用牛津经济研究院和穆迪公司的数据估测了全世界前300大城市的经济产出。 [8] 我和我的团队用这些经济产出数据与人口数据一起估算了人均经济产出。数据虽然不完美,但对全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提供了粗略衡量。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300个城市分为四组,它们覆盖了从最发达的西方城市到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
第一组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地区,它们是赢者通吃城市化的最大赢家,包括超级城市纽约、伦敦、洛杉矶、巴黎、新加坡和香港,知识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先进发展中国家中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这100多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介于45000~94000美元之间,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却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6%。
第二组是发达国家地区中较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30000~45000美元,包括巴塞罗那、柏林、哥本哈根、马德里、墨尔本、迈阿密、米兰、罗马、首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这100个城市地区也占世界总人口的4%,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1%。
第三组是较不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15000~30000美元,包括加的夫、利物浦、那不勒斯以及正在迎头赶上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如曼谷、北京、波哥大、瓜达拉哈拉、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上海等。这70个城市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9%。
第四组是最贫困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仅为4500~15000美元,它们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包含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地区,如马尼拉、雅加达、开罗、亚历山大、德班、麦德林、卡利、孟买、加尔各答、德里以及很多正在城市化的中国贫困地区。这1/3左右的城市地区占了世界人口的4.3%,但仅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3%。
虽然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出现在前三组城市地区,但它显然在第四组城市地区更严重。东南亚有5亿贫民窟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亿,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有1.1亿。 [9] 全世界每天约有20万人迁往城市,到202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达到10亿。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缺少基本服务设施,如冲水厕所、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卫生设施,以及清洁水资源和电力供应。举例来说,非洲只有约一半(54%)的城市居民拥有我们在西方世界习以为常的卫生设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超过2/3的城市居民没有基本的电力供应。世界上最不幸地区和最幸运地区(包括西方城市)在经济资源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惊人差别。对于约10亿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化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许多贫民窟没能提供经济上升的渠道,而是成了自我强化的贫困陷阱。从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和违章居住区、市中心的出租屋和破败公共住房到贫困乡村,贫民窟的居民挤在狭窄破旧的房子里,缺少经济机会。贫民窟往往分布在城市边缘,在地理上十分孤立,远离经济活动。很多地区已经证明,传统经济政策和投资无法扭转现状。举一个近期的例子:2009年,印度宣布采取广泛措施,旨在5年内大力消除贫民窟,但仅仅两年后领导人就不得不承认,在2011—2017年贫民窟人口将增长12%。 [10]
巨型贫民窟之所以长期持续存在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今天绝大部分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都是世界上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一个世纪前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地区则是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地区。第二,如今世界更大,人口更多,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是世界人口中心。第三,很多城市化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争、冲突、极端暴力和自然灾害而集体迁移到其他城市而产生的 [11] ,这类大规模人口迁徙很容易超出城市有效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所以大量新移民最后只能挤在巨型贫民窟里。
第四,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大问题。广泛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发展打破了城市、本地农业和本地工业之间的传统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平衡发展。以前,城市为当地农业提供市场。但现在,城市里有大量全球食品连锁商店,它们不再依赖周围地区提供的农产品。快速城市化的国际化都市中,人们可以以低廉价格买到从其他地方进口的食物。 [12] 全球化还完全打破了城市和本地化制造业发展的联系。以前城市里有一系列围绕居民衣食住行开展的基础工业活动,如开采、制砖、伐木、食品处理等。在现在的全球化经济中,所有这些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业活动不再零散分布在全世界的城市中,而是越来越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无法像从前那样以传统工农业为基础发展经济,它们提供的工作种类也大大减少,无力满足成百上千万新移民实现经济阶层向上流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发达国家考虑全球化影响时,想到的是被廉价外国工厂抢走的制造业工作。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来说,城市化实际上切断了工人经济发展的通道。
全球城市危机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这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迁移浪潮中,城市化已经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了。对于过去几百年的西欧和美国城市来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然而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出现了一个恼人的新现象:“没有增长的城市化”。 [13]
一项研究追踪了过去约5个世纪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具体说明了两者的脱节。研究发现,从1500年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都十分松散。在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爆发性增长之前,世界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只增长12%。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才变得紧密相关,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增长20%。但这一结果可能是发达国家广泛工业化的产物,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还未开始城市化,十分贫穷。到了2010年,这一关系又发生了改变。现在快速城市化的是穷国家而不是富国家,而城市化和增长的关系与16世纪很像,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率的增长只有13%。总之,我们不能继续假设城市化和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已经不是这样了。 [14]
虽然城市化不能确保经济繁荣,但它仍是更优选。即便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它们仍比农村边远地区拥有更显著的经济优势,哪怕是最穷的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也超过边远地区。为了研究这种差异,我和我的团队发明了一个简单指标——城市产出比,它衡量的是城市地区和其所在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之比。 [15]
在典型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城市,城市产出比介于1~1.5之间,说明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至少与其所在国家非城市地区的产出持平,最多高出50%。发达国家中,城市产出比最高的是硅谷所在地圣何塞,达到了1.6,伦敦为1.5,波士顿和旧金山为1.4,纽约为1.3,洛杉矶和巴塞罗那为1.2,东京、法兰克福和芝加哥介于1.1与1.2之间。
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城市产出比非常高。有超过80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是其所在国的两倍以上,包括北京、伊斯坦布尔、孟买、圣保罗和上海等。约50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3~9倍,有12个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10倍以上,包括马尼拉(13.6)、曼谷(12.6)和利马(12.6)等。
但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的数据仅覆盖了全世界最大的300个城市地区,这些地方仅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3(31%)。虽然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没有覆盖到很多其他城市地区,包括最穷、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但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粗略估计。我和兰德公司的计算地理学专家提姆·古尔登一起,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及其他研究机构卫星图中夜晚的灯光对全世界每个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城市产出进行了间接估测。 [16] 把我们称为“光地区产出”的光发射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得到城市产出比,比较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出(包含不确定的城市地区)。图9.1的地图展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注意,反映高城市产出比的大圈出现在非洲、东南亚和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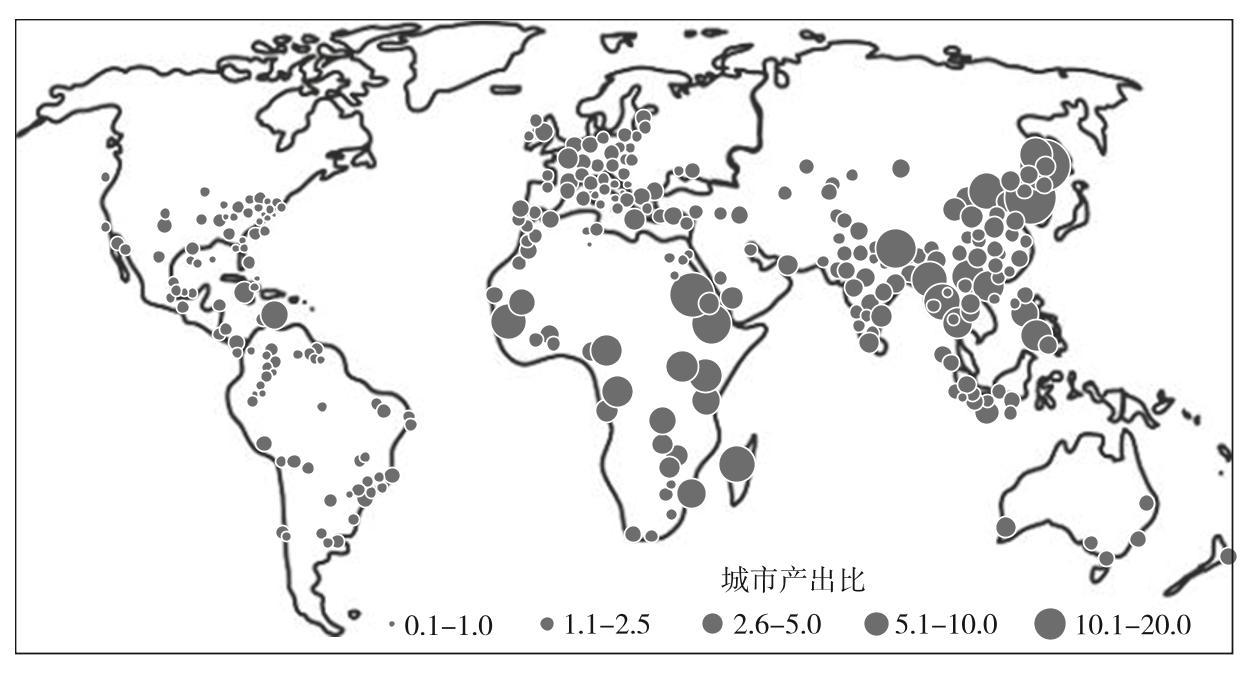
图9.1 城市产出的比较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约瑟夫·帕里拉、耶苏·莱亚尔·特鲁希略、艾伦·贝鲁布和陶然,《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以及来自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和提姆·古尔登的夜间灯光数据,全球大都市:基于夜间卫星图像的城市中心经济活动评估,《专业地理学家》期刊,2010年。
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125个城市产出比超过3的城市地区,其中有40个地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5,7个地区(仍然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10。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城市产出比都这么高,但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比值小于1。即便在地球上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城市中心的生活质量仍然比乡村好。怀疑论者可能会反对说,这种优势更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不是它们城市的高生产力。不过广泛规律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不管城市化有多少弊端,它仍是更优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怎样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并重新将城市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联系起来呢?
答案是,通过释放城市居民的活力和才能,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发展。“找到贫困的‘原因’是行不通的,因为贫困没有原因,繁荣才有原因,”简·雅各布斯写道,“贫困和经济萧条就是缺乏经济发展而已。” [17] 如果缺乏解放人和社区创造力的机制,或者存在阻碍创造力发挥的不良组织,贫困就会出现。反之,能利用人的创造力的机制和组织可以促进繁荣。如果贫困社区的居民能够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技能,他们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经济状况都会得到改善。
1972年,约翰·F.C.特纳在一篇题目特别的文章“作为动词的住房”中比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政府建造廉价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名词的住房”)以及自下而上的穷人自己建造住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动词的住房”)。 [18] 在第一种模式中,穷人被孤立,离经济机会更远,贫困进一步集中,从而带来持续失败。而在第二种模式中,穷人聚集在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地方,更靠近经济机会。
记者道格·桑德斯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强调“落脚城市”的作用。他认为“落脚城市”是帮助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磨炼技能的地方,比如重庆的六公里,它位于中国中部这座1000万人口大城市的郊区,从前是个贫困乡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人们纷纷从周边农村涌入,来这里务工。由于工作有限,人们开始做起非正式的小生意,还开始自己建造房屋,很少有合法的。桑德斯说,今天的六公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群落,它的12万居民已经完全融入重庆市。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外围蓬勃发展的贫民窟,都是临时建筑,街上随处可见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垃圾,但它也是创业的大熔炉,有各种小商贩、小工厂、新移民在这里生产纺织品、塑料、木制品,甚至摩托车零部件。六公里的居民告诉桑德斯:“在这里,只要你找对了谋生方式,就能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 [19]
越来越多的研究记录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在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潜力。人类学家詹妮丝·珀尔曼研究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有140万人口曾生活在这里的1200多个社区中。 [20] 人们普遍认为贫民窟是持续贫困的陷阱,珀尔曼的研究却发现,它们可以变成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载体。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孙辈中,有一半人到21世纪初住上了条件更好的房子,有些是租的,有些是买的,但大部分房子都有电、自来水、室内厕所,很多房子还安装了空调、洗衣机甚至平面电视。贫民窟家庭的教育水平在代与代之间提升速度很快,在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父母辈中有3/4的父亲和90%的母亲都不会读写;2000年,受访居民的子女文盲率只有6%,他们的孙辈则全部都能读写,多数都有高中学历,还有不少人上了大学。贫民窟居民没有陷入注定的贫困,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自我提升,还发展了自己的社区。
圣菲研究所和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的研究则更广泛地证明了这种自下而上模式的有效性,他们让来自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社区居民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开始是在传统纸质媒介上记录,后来则通过移动设备记录。研究发现,虽然贫困社区的穷人有发展潜力,但日常生活的重负让他们无法有效利用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发达国家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分工,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付日常生活的急迫需求:自己取水、交换食物或自己准备食物、长距离步行或乘坐最基本的交通工具。研究结论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提高贫民窟的生产力,就要让城市穷人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21] 在哥伦比亚我常听人提到著名自行车手内罗·昆塔纳的故事,他每天在一辆廉价自行车上骑行10英里山路上下学,就这样锻炼出卓越的爬坡能力。不过他是个特例,大部分人都不能像他这样有效利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间。
另一项研究发现,巴拿马贫困地区的企业家同样面临缺少时间和资源的问题。他们有很多创新的商业想法,但要么是没有钱来完善这些想法,要么是没有时间等待市场发展成熟。这种状况十分堪忧,因为在传统就业岗位不足,并且穷人找工作时面临较严重歧视的地区,自主创业是对传统就业市场的重要补充。 [22]
各项研究都说明,穷人并不缺少技能或创新能力,而是缺少能有效利用它们的时间和资源。贫困社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帮助居民与社区利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更糟糕的是,很多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散漫扩张孤立了穷人,斩断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大量从农村地区涌入新兴城市的穷人聚集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和临时居所,远离市中心的发展机会,这种情况在非洲尤甚。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密集,如开罗、德里、加尔各答、马尼拉和孟买,但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正以远高于西方发达城市的速度向外散漫扩张。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什洛莫·安格尔的研究说明,在1990—2015年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总城市人口数量翻了一倍,但占地面积增长了350%,人口密度实际上大幅下降52.5%。如果它们仍以这样的速度扩张,从现在到2050年,这些城市的占地面积还将扩大4倍。 [23]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连通性。增加公路和基本交通等基础设施,穷人就能靠近发展机会,城市的市场规模也能得以扩大。非法居住场所占据了大量空间,它们的平均街区面积大于发达城市居民区,而道路面积则相对不足。例如,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道路仅占城市面积的12%,远低于发达城市的比例。
街道是全球贫民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要素,它们不仅能让居民在城市各地穿行,还是建设其他重要实体基础设施的前提,如水管、下水道和电线等。另外,街道还将贫民窟及其居民与城市的种种便利条件相连。联合国人居署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街道能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它能吸引商铺和服务业,增强居民对居住社区的认同感,提高社区安全感,带来更规范的发展”。 [24] 正规的街道地址能将非法占据的住宅变成合法住宅和正常运转的社区,这一转变又能促进商业发展并提高流动性,因为房子可以交易了。随着社区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贫民窟就能从孤立的贫困陷阱转化为通向经济机会之路,从而更全面地融入城市经济生活。
交通系统也能有力增强社区之间的连通性,并连通居民与经济机会。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城市,轻轨向当地贫民窟居民开放了经济机会,提高了轻轨站周边的人口密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降低了当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汽车的依赖度。 [25]
传统轨道交通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更廉价、更符合当地情况的交通方式也可以增强社区连通性。2011年我和创意阶层咨询公司的同事参与评选了首届“菲利普斯宜居城市奖”,三个获奖创意之一是“遮阳站”,在坎帕拉、乌干达和其他快速发展的非洲城市,它不仅可以用来遮阳避雨,还能作为小型巴士和简易公交车的车站,这些交通工具给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在麦德林还看到了一些提高当地连通性的巧妙方式。不久以前,麦德林还被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和他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控制,是世界上最混乱暴力的城市之一。13区那时是麦德林最贫困危险的社区,由于海拔的原因,它远离市中心、就业和教育资源,那里的12000名居民要穿过相当于28层楼高的斜坡和楼梯才能进出社区。山坡上其他拉丁裔贫困社区的居民则每天要坐长达4个小时的巴士上下班。后来,市政府安装了连通13区和城市其他地区的户外电梯,以及连通其他贫民窟和市中心的空中缆车。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社区群体将电梯和缆车站周边区域改造为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商业活动、社会与公共服务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些小的改进把孤立且长期贫困的贫民窟变成了更安全、功能更完善和经济更连通的社区。2012年,麦德林被城市土地学会、花旗银行和《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年度创新城市。 [26]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基础设施的战略性投资有利于连通贫民窟居民和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居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把城市孤立和贫穷的恶性循环转化为城市进步的良性循环。
城市新居民、社区与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很多努力来促进发展,但是光靠他们是不够的,国际发展政策必须以城市和城市建设为核心,毕竟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在于城市而非国家。2015年,联合国将“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作为17个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 [27]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是要解决这些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全球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包含并影响了如天气变化、能源使用、贫困和经济机会等各类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只有学会建设更有生产力、更繁荣、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城市,我们才能解决其他挑战。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方法、信息和数据。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医药、法律、工程和商业等几乎其他所有领域相比,在城市学领域,告诉市长和城市建造者如何建设社区与城市的系统性培训少之又少。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得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由于缺少追踪监控全球城市地区发展的基本数据,我们甚至无法鉴别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不可行。可靠、连贯和完全可比的数据对于我们重建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连接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城市学可以借鉴医药学的发展经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开始加强医药与科学研究的联系,并制定了医生、医学专家和公共健康官员共同遵守的最高水准的临床协议书。医生在医学院要学习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其他领域的知识,还要作为实习生接受大量的在职培训,并定期持续地参加会议。新药和医学干预方式要经过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全球医药和公共健康机构网络保证新知识能得以快速高效地传播。我们应有类似的机构来培养城市建设者,并建立类似的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全流程,将基础数据和最佳实践中提取的先进知识输送到全球的市长、社区建设者和城市领导人手中。
在22世纪,我们投入新建与重建城市的资金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在这方面花费资金的总和。但我们只有给予城市应有的关注和它们迫切需要的资源与投资,城市才能成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希望之光。
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
[1] Medellín Declaration, “Equity as a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联合国人居署, Seventh World Urban Forum, April 2014,http://wuf7.unhabitat.org/Media/Default/PDF/Medell%C3%ADn%20 Declaration.pdf。
[2] Joseph Parilla, Jesus Leal Trujillo, Alan Berube, and Tao Ran, Global Metro Monitor,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5,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
[3]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定义,贫民窟是居民缺乏以下一种或多种资源的地方:清洁水、厕所、安全的住房、充足的居住空间(居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人数不超过两个)、不被迫迁或驱逐的合理保障。参见联合国人居署,Streets as Tools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lums: A Street-Led Approach to Citywide Slum Upgrading, 联合国人居署, 2012, http://unhabitat.org/books/streets-as-tools-for-urban-transformation-in-slums, 5。
[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Urban World: Mapp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Cities, March 2011, www.mckinsey.com/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_world.
[5] Brandon Fuller and Paul Romer, “Urbanization as Opportunity,” World Bank, 201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3/11/18868564/urbanization-opportunity, 1–13.
[6] 关于到2030年的数据预测,参见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Metropolitan Century: Understanding Urbanis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Paris: OECD, 2015), www.oecd.org/greengrowth/themetropolitan-century-9789264228733-en.htm。关于到2150年的数据预测,参见Robert H. Samet, “Complexity, the Science of Cities, and LongRange Futures,” Futures 47 (2013): 49–58。
[7] 使用的参照物是2015年16GB的iPhone. 参见The comparison is for a 16GB iPhone 6 in 2015。参见 Catey Hill, “This Is How Long It Takes to Pay for an iPhone in These Cities,” Marketwatch, September 24, 2015, www.marketwatch.com/story/this-is-how-long-it-takes-to-pay-for-an-iphone-inthese-cities-2015-09-24。
[8] Parilla et al., Global Metro Monitor.
[9] 联合国人居署,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http://mirror.unhabitat.org/pmss/listItemDetails.aspx?publicationID=3387。好消息是发展中国家中在贫民窟生活的城市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2%,这意味着约2.27亿贫民窟人口获得了更清洁的水和卫生资源与更好的住房。坏消息是全球贫民窟人口总量与发展中国家急剧上升的人口同步上升了。参见联合国人居署,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New York: Routledge, 201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1143016_alt.pdf, 7。也参见联合国人居署,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6/05/WCR-%20FullReport-2016.pdf; Eugenie L. Birch, Shahana Chattaraj, and Susan M.Wachter, eds., Slums: How Informal Real Estate Markets Work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10] “UPA’s Target: A Slum-Free India in 5 Years,”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5,2009,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UPAs-target-A-slum-freeIndia-in-5-years/articleshow/4618346.cms?referral=PM.
[11] Benjamin Marx, Thomas Stoker, and Tavneet Suri,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4 (2013): 187–210.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Edward Glaeser, “A World of Ci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rbanization in Poorer Countries,” Paper no. 1974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www.nber.org/papers/w19745;Richard Florida, “Why So Many Mega-Cities Remain So Poor,” CityLab,January 16, 2014, www.citylab.com/work/2014/01/why-so-many-megacities-remain-so-poor/8083.
[13] Remi Jedwab and Dietrich Vollrath, “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7 (July 2015): 1–94.
[14] Ibid.; Richard Florida, “The Problem of Urbanization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CityLab, June 12,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6/theproblem-of-urbanization-without-economic-growth/395648.
[15] Richard Florida, “Why Big Cities Matt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ityLab,January 14, 2014, www.citylab.com/work/2014/01/why-big-cities-matterdeveloping-world/6025.
[16] 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im Gulden, “Global Metropolis: Assess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 no. 2 (2010): 178–187。关于利用卫星数据估计经济产出,参见J. Vernon Henderson, Adam Storeygard, and David N. Weil,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no. 2 (2012): 994–1028. As they note, “Night lights data are available at a far greater degree of geographicfineness than is attainable in any standard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17]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18] John F.C. Turner, “Housing as a Verb,” in John F.C. Turner and Robert Fichter, eds., Freedom to Build: Dweller Control of the Housing Proc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19] Doug Saunders, Arrival City: How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istory Is Reshaping Our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2010); Doug Saunders, “Liu Gong Li: Inside a Chinese Arrival City,” Arrival City video, n.d., http://arrivalcity.net/video.
[20] Janice Perlman, Favela: Four Decades of Living on the Edge in Rio de Janeir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nice Perlman, “Global Urbanization and the Resources of Informality: Moving from Despair to Hope,” Presented at the Humanity, Sustainable Nature: Our Responsibility Workshop, Vatican, May 2–6, 2014.
[21] “SFI Takes First Steps Toward a Science of Slums,” Santa Fe Institute,February 6, 2013, www.santafe.edu/news/item/gates-slums-announce;Rebecca Ruiz, “Scientists Loo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lums Devise a New Way to Look at Big Data,” Txchnologist.com, January 22, 2013,http://txchnologist.com/post/41201839670/scientists-looking-to-solve-theproblem-of-slums; Luis Bettencourt, “Mass Urbanization Could Lead to Unprecedented Human Creativity, but Only If We Do It Right,” Huffington Post, August 29, 2014, www.huffingtonpost.com/luis-bettencourt/massurbanization-creativity_b_5670222.html?1409329471.
[22] 研究呼吁通过小额拨款或企业孵化器的方式扶持城市贫困企业家发展和扩大初创企业。Laura Doering,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somorphism: Poverty and Market Creativity in Panama,”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2, no. 3 (Fall 2016):235–264; Phyllis Korkki, “Attacking Poverty to Foster Creativity in Entrepreneurs,”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3/13/business/attacking-poverty-to-foster-creativity-in-entrepreneurs.html.
[23] 有关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和密度的数据,以及本段内容都来自Shlomo Angel, Atlas of Urban Expans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6。
[24] 联合国人居署, Streets as Tools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lums。
[25] Mark Swilling, “The Curse of Urban Sprawl: How Cities Grow and Why This Has to Change,” The Guardian, July 12, 2016,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jul/12/urban-sprawl-how-cities-grow-change-sustainability-urbanage.
[26] Letty Reimerink, “Medellín Made Urban Escalators Famous, but Have They Had Any Impact?,” Citiscope, July 24, 2014, http://citiscope.org/story/2014/medellin-made-urban-escalators-famous-have-they-had-any-impact; “City of the Year,” Wall Street Journal Magazine, 2012, http://online.wsj.com/ad/cityoftheyear.
[27]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是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个,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你上次看到国家领导人把城市或城市政策列为重要议程是什么时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生长在城市,自然十分关心城市问题,但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城市政策上取得什么进展。2016年有两位前市长参与了民主党党内初选——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前市长伯尼·桑德斯和前巴尔的摩市长马丁·奥马利。另外,里士满前市长蒂姆·凯恩加入了希拉里的竞选阵营。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和总统竞选中,除了我协助奥马利起草的有关城市政策的呼吁,几乎再没人提到城市政策。上一次有关城市问题的严肃国家对话还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旧城市危机时期,有的城市爆发暴乱,有的濒临财政崩溃。现在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政客谈到城市问题时,都在指责自由主义在解决城市长期贫困与犯罪问题方面的无能。现在与实际城市政策最相关的呼吁就是通过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1]
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这种强烈反差令人忧心。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取决于人才、企业和其他经济资产在城市的聚集。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我们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活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
但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城市面临的深刻挑战可能影响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聚集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分裂了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意味着少数赢家获得绝大多数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成果,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发展停滞,被赢家远远抛在身后。随着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城市、郊区和整个美国都变成了一块由集中优势地区和集中劣势地区构成的拼布。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孤立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危机,它也是当代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影响范围覆盖全美国——从超级城市、科技中心到“铁锈地带”老工业城市和“太阳地带”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图10.1和表10.1展示了美国各大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能捕捉新城市危机的全貌,但这一综合性指标衡量了危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经济隔离、薪酬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高住房成本。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料,危机在前两大超级城市和领先科技中心最严重:超级城市洛杉矶的指数最高,纽约第二,旧金山第三。科技中心圣迭戈、波士顿和奥斯汀也排在前十。更详尽的统计结果巩固了这个结论——新城市危机指数和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还与高科技行业的聚集、创意阶层人口占比、大学毕业生人口占比、经济产出、收入和薪酬水平呈正比。新城市危机也与美国的政治分化密切相关——它与2016年希拉里支持者的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与特朗普支持者的占比呈负相关。我们再次看到,新城市危机是人口更密集、经济更发达、更自由主义、受教育程度更高、高科技发展程度更高,以及拥有更多创意阶层群体的大城市地区的基本特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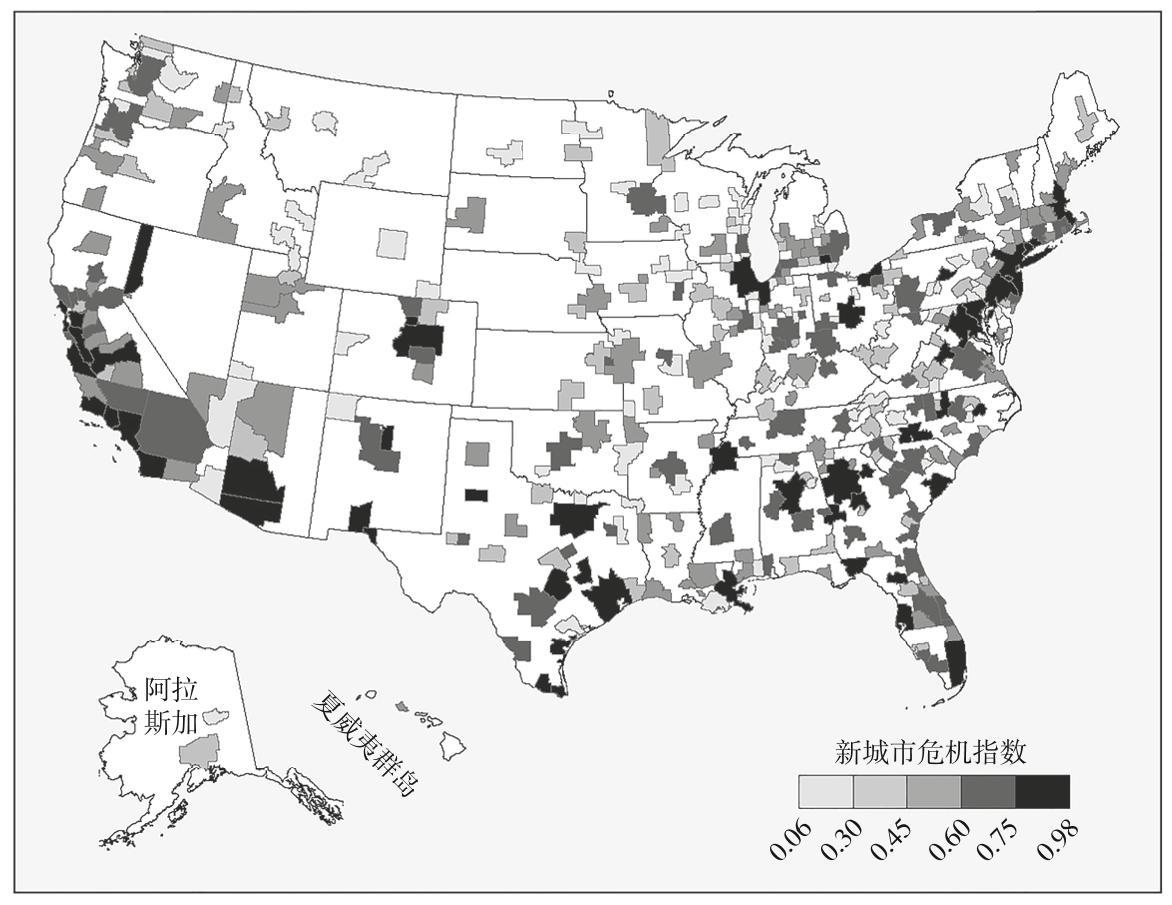
图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1)
表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另一方面,危机也出现在美国众多其他地区。芝加哥、迈阿密和孟菲斯也位列新城市危机指标排行榜的前十,“太阳地带”的达拉斯、休斯敦、夏洛特、亚特兰大、菲尼克斯、奥兰多和纳什维尔排名稍后,“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底特律排名靠前。如果把较小城市地区也包括在内,新城市危机指标数最高的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诺瓦克地区,圣塔芭芭拉、弗雷斯诺、特伦顿、里诺也排名靠前,其他一些小型大学城也是。
新城市危机影响范围之广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焦虑持续恶化。郊区发展模式曾是美国梦的基石,而现在它的瓦解重创了中产阶级群体,还让穷人和弱势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也觉得自己没有以前富足了,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保障自己和后代未来的稳定生活变得越来越昂贵,也越来越困难。
实际上,美国经济之所以无法从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甚至陷入“长期停滞”,主要就是因为新城市危机。“长期停滞”的概念最早是指经济体失去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创造力、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如今,用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的话说,我们陷入了“新萧条”时代,经济复苏速度不理想,高薪就业岗位也不足以重振广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3]
包括萨默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增加政府基建支出来刺激经济,这个想法是有成功历史先例的。 [4] 19世纪,运河和铁路将美国连为一体,拓展疆土,刺激经济发展与创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有轨电车和地铁进一步刺激城市发展,拓展城市的人口容量。20世纪中期,对公路和个人住房的大量投资带来大规模郊区化发展,经济增长期也随之延长。
现在,加大公路和桥梁投资也许能短暂地刺激经济,但很难带来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胡乱安排的基建项目,而是能促进聚集化、集中化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投资。若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重振经济,就必须成为更远大的聚集化与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新城市危机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从很多方面标志了大规模美国拓荒潮的终结。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著名演讲中说:“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入新世界水域的第一天开始,美国人就一直在永不停歇地拓荒,这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使命。”他说,美国的西部边疆终于关闭了,国家的基础时代也随之终结。然而,事实证明他言之过早,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用历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的话说,郊区的“马唐草边疆”成为美国新的增长中心。 [5] 新城市危机标志着这段漫长的廉价外向型增长时代的终结。
如今向外扩张已经不能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了,这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要重振美国经济,就要实现城市和郊区的聚集化和密集发展。与上个时代的廉价扩张型增长相比,这种再城市化所需的投入更高。提高城市发展的密度以满足聚集需要,修建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来巩固发展,重建高密度郊区,按需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等,这些需要投入的成本都远高于修路和随意建造郊区独立屋。
除了高成本之外,美国社会始于托马斯·杰斐逊的田园幻想的反城市偏见根深蒂固,再城市化明显与之相悖。反城市化偏见仍深深根植在国家立法机构和国会中,给予了郊区和农村地区过多的权力。 [6] 偏见被一种由来已久的保守派主张所削弱了,即城市是精英化、浪费、放荡、犯罪的代名词,也是导致社会瓦解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而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强化了这种偏见,即传统美国梦的经济适用住房更主要分布在散漫扩张的保守地区,而不是密集和知识型的自由地区(2015年,蓝州的平均房价几乎是红州的两倍,分别为每平方英尺227美元和119美元)。 [7]
重振政治决心来应对新城市危机并不是件容易事,在如今特朗普执政、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但现在是美国发展的必要转折时刻,这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应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才能把经济和社会带回正轨?
我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但此前我们对新城市危机的了解一直非常片面,提出来的战略和方案很不完整,难以全面应对危机中方方面面的深层挑战。正如很多人所说,我们必须要克服我称之为新城市卢德主义的保守“邻避”冲动,因为它不利于提高城市创新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聚集度和密度。当然,也应该改革过于严苛、不利于提高聚集度的分区和建筑法规。毫无疑问,城市领导人应当获得更多权力来治理城市。但这些还不够,要想全面应对新城市危机,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要解决一个如此深入和系统性的危机,我们必须把城市和城市化放在经济繁荣议题的首位。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危机源于城市,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要恢复广泛和可持续经济繁荣,就必须使美国的城市化更全面、更平等。这需要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但不是不可能。好消息是,仅利用我们手头现成的资源就能大有收获。要提高生产力、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围绕以下七个方面铺开新战略,我将对它们进行逐个讨论。
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
聚集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利用聚集力来最大化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用至关重要。正如我们看到的,问题的症结是城市土地关系:越是需求旺盛的地方,土地越是稀缺。我们无法创造出更多土地,但我们能提高土地开发的密度和效率。
越来越多所谓的市场城市规划专家提出,提高土地开发密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部分限制性分区和建筑法规,它们限制了市场供给,导致建筑供不应求。他们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分区和建筑法规确实需要放宽和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再让邻避和新城市卢德分子阻碍城市和经济所急需的高密度和高聚集化发展了。
解除土地管理限制虽然必要,但不足以解决新城市危机的问题。尽管此举能增加新建房屋,提高城市密度,但城市土地和高层建筑的成本高昂,解除土地管理限制的后果是将产生更多高级高层公寓,而不是廉价住宅,而后者才是城市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对这一举措提出过明确质疑:“随着新建房屋的增加,城市经济产出会提高,土地仍是稀缺要素,最后租金仍将十分高昂。”他写道:“如果我们解除建筑管理限制,土地所有者将成为最大赢家。” [8] 最后,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反而只能从中受益最少。
另外,作为“太阳地带”散漫扩张城市的典型,休斯敦没有分区和土地使用限制,开发商可以自由选择建筑地点和建筑种类,是扩张性城市的原型。但是在不平等、隔离和新城市危机的排行榜上,休斯敦和纽约、洛杉矶与旧金山总是靠得很近。大休斯敦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十一;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四,仅次于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三,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虽然休斯敦的房价比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低,但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城市,休斯敦的不平等和隔离水平也位于全国前列。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某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特有的危机,更是普遍存在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的危机。解除土地使用限制,让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变得更像休斯敦,很难将城市从新城市危机中解救出来。
另外,完全解除土地使用与房屋管制有杀鸡取卵的风险。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是住宅密集的摩天大楼,而是能促进融合与互动的多功能中高层建筑。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创新实力最强的不是纵向扩张、摩天大楼密集的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而是纽约、旧金山和伦敦。曾是老工业区的社区,街上主要是中高层建筑、工厂和仓库,偶有高楼,这些带来持续的融合与互动。很久以前简·雅各布斯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缺少步行空间,多样化就成了大问题。” [9]
完全放松土地使用管制可能会鼓励过度的垂直扩张,将城市变成死气沉沉的“公寓峡谷”,破坏最富创造力的城市社区。因为在郊区发展时代,这类城市社区的建设完全停滞了,现在它们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每消灭一个,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创新资产。
虽然落后的法规必须淘汰,但不能破坏宝贵而独特的城市生态系统。因此我们要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使之具备灵活性以适应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并能增强城市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而不是破坏它们。
要实现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目前对房产税的依赖,以土地价值税取而代之。房产税以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筑物为征税对象,而土地价值税以土地本身的基础价值为征税对象。这样能极大地鼓励不动产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他在18世纪早期就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源于土地的非劳动收入是一种纯粹的浪费。
土地价值税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19世纪末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说,土地价值税不仅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还能提高工资、降低不平等并提高生产力。其基本前提是,土地开发程度越低,对其所征的税率越高。乔治认为,对未开发土地的征税应为土地价值的100%减去业主对土地进行改良获得的增值。换言之,如果没有对土地进行改良,那么就应该把全部的土地价值都返还给公众。按这一税收制度,在今天的城市,未开发的地面停车场会被征收极高的税,小型公寓楼的税率较低,较大公寓楼的税率更低。这种税收制度激励业主提高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 [10]
此外,在目前的房产税制度下,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不仅没有动力提高房地产开发密度,还能从邻里升级和房地产升值中获得超额回报。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大大提升了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值,但结果是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敛得了意外之财,公园和周边社区几乎没有从中受益。类似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吸引了新居民、新餐馆、新咖啡店、新的好学校并且犯罪率下降的城市社区,而土地价值税能让更广泛的公众群体分享社区改善的好处,因为源自整体社区改善的土地价值上涨被征税并返回给了公众,能用于投资公共服务,缩小社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是,通过地方税收政策来团结邻避者共同促进社区新发展。这一基本理念称为“增值税本地转移”,它允许社区居民分享新发展带来的税收收入——比如在一段时间内抵扣和减少居民自己缴纳的房产税。 [11]
虽然这样改变国内税收制度看起来很有政治难度,但土地价值税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正反两派城市学家的广泛支持,它能让更多房屋被建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使城市和经济更强大。
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
基础设施是解决城市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对其进行良好规划和战略性投资,能扩大聚集发展的规模,帮助更多地区实现聚集化发展,并加强偏远地区与城市聚集发展地区之间的联系。
基础设施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所有政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话题,特朗普呼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刺激经济。加拿大的贾斯廷·特鲁多政府也承诺投入巨额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基建项目都能奏效的,投资修建更多道路和桥梁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我们需要进行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更加分散,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将基建投资从使人们更加分散的公路转移到聚集人与经济活动的公共交通。
美国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少得惊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公共交通基本都是100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产物(纽约和伦敦的大规模公共交通基本都建成于汽车出现之前)。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十分稀缺,地铁和公车站附近的地价和房价才如此高昂。研究显示,有公共交通的社区让居民的通勤更便捷,从而更容易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扩大公交系统能增加这种社区的数量,让更多人,特别是相对弱势群体得以享受这种便利。
公交系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能发挥最大效用,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这些城市已经有公交系统了,但还需要更多公共交通将偏远地区和市中心相连,减少交通拥堵和对汽车的依赖。
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也需要公共交通,面积过大、发展已经超负荷的城市尤其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随着城市扩张,其发展将面临地理限制。当城市人口达到了500万或600万的临界值时,汽车和公路就不再是很有效的交通方式了。美国有不少这种规模的城市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大华盛顿、波士顿、费城、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这些城市地区已经临近或到达了依靠汽车实现地理扩张的极限,要通过进一步向外扩张来增加住房供给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提高市中心和郊区的密度是唯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不论是在城中心还是郊区地带,要实现更密集、更有聚合力的发展,关键都在于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并减少汽车依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亮点是,很多地区的选民都投票支持增加政府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扩大城市外围。在20世纪中期,有轨电车、地铁和汽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的产生扩大了工人的通勤范围,使城市地区得以向外扩张。高铁等更好更快的公共交通能极大地扩张城市地区的通勤和工人居住范围,让他们能住在廉价地段,去更富于生产力的地段工作。
不是所有在超级城市或知识中心工作的人都得住在那里。我在第二章中提到一项研究展示了土地使用限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我还提到有效的交通系统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方便工人在住房成本低廉的偏远地区和城市中心之间通勤。研究者称,交通系统(尤其是高铁)能在顷刻之间扩大城市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无须处理棘手的土地使用限制问题,甚至可能也无须增加新住房。 [12]
高铁还能连接大型都会区中的各个分散城市。 [13] 类似的连接已经出现在还没有高铁的地区了,比如,美国铁路公司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连接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这整片地区的人口超过5000万,经济产出超过20亿美元。美国有十几个这种大型都会区。在五大湖地区,有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在内的中东部城市集群,还有从布法罗、罗切斯特到多伦多及其附近地区的一系列城市集群;在南方,有迈阿密-坦帕-奥兰多地区、亚特兰大和夏洛特地区,以及包括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等城市的得克萨斯三角地带;在加州,南部有以洛杉矶为中心的都会区,北部有以旧金山为中心的都会区;在太平洋西北地区,有包括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在内的卡斯卡迪亚地区。
高铁能缩短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促进城市的紧密连接。真正的高铁[行驶速度能达到法国TGV(高速列车)或者日本新干线的水准]能将纽约与波士顿或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的交通时间缩减到90分钟,用同样的时间也能从达拉斯到休斯敦或奥斯汀。洛杉矶与旧金山,或匹兹堡与芝加哥之间的通勤时间能缩短至2.5个小时。 [14] 高铁能显著扩大这些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经济市场,提升它们的整体经济竞争实力。
私有部门投资已经开始进入高铁项目了。佛罗里达政府不愿插手,一些私人投资者便自行恢复了迈阿密和坦帕之间的部分高铁线路。然而,最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将更多汽油税收入投资于交通系统特别是高铁建设。
应当减少以修建公路的方式给汽车的直接补贴,使公共交通领域重回平衡。伦敦等城市已经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让汽车驾驶者付费使用繁忙道路,解决交通、散漫扩张和污染问题。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电动汽车和优步、来福车等线上按需运载平台将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仍需要公共交通作为连接网,提高城市聚集度,建设更多让人住得起的密集的多功能聚集社区。最后,重点不是选择哪种交通方式,而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居民交通、提高城市密度、让更多人有房可住,以及刺激整体经济发展。
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
廉价住房是解决新城市危机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在最昂贵的城市中,除了社会经济状况最好的1/3人口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无力承担高昂的住房成本。警察、消防员、教师、医疗人员、餐厅和零售工作人员等基本服务从业者都被迫迁到远离市中心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心的偏远地区。在有的城市,吸引这些基本服务从业者越来越难,大型商业开发商呼吁修建“城市劳动力住房”,保证有足够多的工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缺乏廉价住房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经济运转的绊脚石。
住房问题可能在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最为严峻,但它的辐射范围远不止于此。太多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租房者,住房开销占收入的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住房系统非常偏好散漫扩张郊区的独立屋,而抑制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需要的聚集式出租屋。
问题主要在于美国的住房政策本身。我们现有住房政策起初的设计意图是刺激郊区化发展,为购房者提供大量补贴。联邦政府每年通过房贷税收减免为购房者提供了约2000亿美元的补贴,如果再算上间接成本,补贴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这是国家每年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房补助(460亿美元)的4~12倍。 [15] 收入最高的20%人口获得了75%的购房补贴,最高的1%人群则获得了15%。这种政策扭曲了房地产市场,导致分散的独立屋过多,而聚集的租赁房屋过少。
即便如此,已经出现了人口从郊区独立屋向多家庭租赁屋转移的现象,我称之为“大住房重置”。自有住房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峰值开始大大降低,现在仍在下降。 [16] 在过去1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变成了租房者,尤其是房价高企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居民。2005—2015年,美国的租房家庭数量上升了900万,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0年涨幅。到2015年底,4300万美国人都在租房,租房者的人口占比从31%上升到了37%。年龄分布在18~34岁的“千禧一代”中有超过70%都在租房。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超过一半市民在租房。 [17]
房屋租赁比住房自有更能满足城市化知识型经济的需要。租房者更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乘坐公共交通上班,而郊区自有房屋者则倾向于长距离开车通勤。租房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创新水平更高,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更高,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人口占比更高,薪酬、收入和生产力也更高。而自有房占比更高的城市地区则相反,创新水平、生产力、多元化程度、高学历和技术人才的人口占比都较低。 [18] 增加租赁房屋、减少独立屋不仅符合城市聚集的需要,还能强化这种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城市聚集。
尽管如此,很多租房者承担着极高的房租负担,陷入房租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死循环中。在2006—2014年,平均房租上涨超过22%,而平均工资收入下降近6%。2001—2014年,房租超过收入1/3(高房租负担的临界值)的人口数量从1480万上升到2130万,而房租超过收入一半的人口数量从750万上升到1140万。低收入租房者(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其中近3/4(72%)的人支付的房租超过收入的一半。2006—2014年,收入底层家庭的房租收入比从55.7%上升到惊人的62.5%。
应重新分配联邦住房补贴,向真正需要的人倾斜,更多地补贴经济状况较差的租房者,而不是经济状况较好的自有住房人群。这样有助于扩大租房需求,鼓励建造更多公寓楼并促进聚集化发展。继续补贴独立屋业主的不平等政策,只会带来更多散漫扩张,破坏密度和聚集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其他成本。
这些措施与理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交通系统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鼓励社会建造更多价格低廉、聚集程度较高的公寓楼和出租屋,但仍不足以解决经济状况较差人群的住房负担问题,特别是在昂贵的超级城市。2016年一项针对旧金山湾区的研究发现,要解决该地区的住房负担问题,需要将更多的市场化住房建设和补贴住房建设结合起来。 [19]
关于如何为真正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廉价住房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如扩大租金调控范围、修建更多政府补贴住房和所谓的包容性区域划分——开发商必须修建经济适用房,才能开发更大、更高和更高端的住宅项目。虽然这些政策的目标很美好,但它们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租金调控会使业主丧失改善不动产的动力,还很容易被钻空子;包容性区域划分在昂贵的超级城市房地产市场最有效,因为它们的开发商愿意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换取修建高楼的许可,但是在其他城市,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开发商减少住房供给;其他大规模改革措施——如开放过时的分区和建筑规则、用土地价值税取代房产税或者扩大交通系统,虽然可以增加总体住房供给,但无法将足够多的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服务业工人和穷人。
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不论是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下一节的内容),还是以住房抵扣的形式直接提供政府支持,甚至通过更广泛的支持政策,比如用负所得税保证基本最低收入(将在再下一节展开说明)。
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
要同时实现提高密度、增加交通基建投资和修建经济适用房三项措施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彻底解决新城市危机。现在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来支持新中产阶级,我们需要更多较高收入的就业帮助人们脱贫,提高居住质量。可能有人会说特朗普和共和党就在做这件事情,但联邦政府、市政府和私人部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政客提出的重塑中产阶级的措施对解决问题没什么帮助。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人都爱把“将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挂在嘴边,但如今只有20%的美国人从事蓝领工作,而在工厂从事直接生产工作的甚至只占劳动力的6%。即便我们能把更大量的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即便被广泛宣传的高级制造和所谓的“作坊制造”还能继续扩张,新的就业岗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在今天的全球化科技经济中,制造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成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力量和支柱了。
另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提议是让更多人上大学。它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对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但这个措施也很难帮助中产阶级恢复昔日荣光,因为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工作岗位——只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高薪知识型和专业型创意阶层工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经济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部门是低薪服务业。超过6000万美国工人在从事低技能水平、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总数占全国劳动力的45%。如果再加上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临时工作的、未充分就业的、失业的以及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则占到了美国劳动适龄人口的2/3。如果我们想创造新中产阶级,就一定得将数千万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薪酬更高的工作。
乍看之下这个提议显得有些古怪,实则不然,它和我们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蓝领工作是差不多的。当时亨利·福特提出了“流水工作线工人的薪水应足够买车”的观点,直击问题要害。我父亲13岁时辍学去工厂上班,那时候他的父母、6个兄弟姐妹和他自己一共9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当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回来进入同一家工厂工作时,发现旧工作的薪水已经足够他养活一家四口、买房,并把我和我弟弟送进教会学校和大学。他的工作和成百上千万份其他工作得以成功转型是得益于罗斯福新政和一些提高制造业工资的项目,包括1935年通过的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与雇主集体谈判权利的《瓦格纳法案》、同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它们共同构成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美国社会推出了新政策,创立了新机构,将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薪酬更高的中产阶级工作,今天我们要用一样的方式转变成百上千万占据社会阶梯底层的服务业工作。
我们可以先从提高最低工资入手。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联邦政府合同工的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10.10美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对于生活成本高昂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来说还远远不够。在洛杉矶、纽约和西雅图等发达城市之外,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带头提高了当地最低工资。2014年中期选举时,阿拉斯加、阿肯色、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这四个深红州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全国前列(剔除各地生活成本差异后)。
保守派通常会提出反对意见:提高最低工资会提高劳动力价格,把更多人挤出劳动力市场。但根据最近的研究,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当前工资中位数的50%左右并不会产生这种负面影响。 [20] 并且我们不该忘记,1968年联邦最低工资是当时工资中位数的55%。
全国各地的住房成本迥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到地域差异,就像其他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政策一样。 [21] 如果我们把最低工资设置在当前本地工资中位数的50%,那它在不同州、不同都会区和不同城市都会不同,最高的是圣何塞,最低小时工资约为15美元,旧金山的约为14美元,波士顿、纽约和西雅图的约为13美元,在更便宜的城市地区,如拉斯维加斯、路易威尔、孟菲斯、迈阿密、纳什维尔、新奥尔良、奥兰多、圣安东尼奥和坦帕等,最低小时工资则为约9.5美元。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把大量低薪服务业工作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工资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但也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工资福利较差的工人缺乏工作积极性,工资低的企业往往要为高人员流动性问题付出高昂代价。相反,待遇较好的工人工作积极性更高,还能带来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很久以前就发现,支付高工资、提高员工工作参与度可以激发创新、提高工厂生产力,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22]
很多事实表明,在服务业提高工人工资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过去几十年,许多成功的零售和酒店管理企业[如乔氏超市、好市多、Zara(服装品牌)、全食超市、四季酒店等]给员工支付的工资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和竞争对手,这是它们“好工作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力,降低人员流动性和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23] 升级低薪服务业工作还能给工人、企业和整体经济带来其他好处: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生产力和利润提升,成百上千万服务业工人的工资提高能极大地拉动消费需求,服务业企业的业绩提高还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提高服务业薪资还能以其他间接方式提高创新力。对我的创意阶层理论最好的评论之一来自一位奥斯汀的创意阶层人士:城市创意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薪水较高的服务业工作。他指出,总部在奥斯汀的全食超市为当地艺术家和其他创意阶层群体提供了大量工作时间灵活、工资较高的就业机会,它对奥斯汀创意经济的支持力度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的支持。 [24] 提高服务业薪资能帮助创意阶层支付房租,从而促进创新经济发展。
升级服务业工作不一定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由于问题部分在于很多企业都没有意识到升级服务业工作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因此政府可以仿照从前在农业和制造业扩张项目和鼓励私人部门成就的奖励项目(如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中扮演的角色,帮助宣传经济中相关的最佳实践。
最后,创造新中产阶级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将为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可以再次参考罗斯福新政时代——大萧条后,我们集体为汽车和家电支付溢价,从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如果过去我们愿意为那些耐用商品支付溢价,支撑起我们父母辈的中产阶级,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帮我们照顾小孩和老人、给我们提供重要服务的人支付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中产阶级。
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
新城市危机最危险的部分可能是城市和郊区中长期集中贫困的蔓延,要解决危机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我们目前有两种消除贫困的方式:一种方式“基于人”,为贫困家庭提供资源,或帮助他们搬到更好的新社区;另一种方式则“基于地点”,通过投资于学校、提供社会服务和降低暴力犯罪来改善贫困社区状况。这两种方式都应为我们所用。
我们知道,如果让贫困社区的家庭搬到教育质量和经济条件更好的社区,孩子们的发展机会将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显然不是每个长期贫困地区的人都能搬到学校更好、机会更多的新社区的,迁移的机会本身就不够多,还有人更愿意留下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如果只让表现最好或来自积极性最高的家庭的孩子搬走,最终就会榨干贫困社区的顶尖人才,剩下的人将面临更严重的集中贫困。
要解决数十年的长期贫困问题还需要对贫困社区进行全面、协调的地区投资。作为美国集中贫困问题方面的顶级专家,罗伯特·桑普森呼吁“为社区采取积极行动”,让每个社区都能给居民提供经济机会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他恰当地指出“贫困居民最想要的不是搬家,而是社区重振。” [25] 地区投资不能像挤牙膏一样碎片化投入,而应提供全面的重要社会和经济服务,覆盖教育和经济机会与降低暴力犯罪等领域。
解决城市的学校问题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中之重。很多贫困社区的学校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无法为学生提供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维生技能,辍学率持续高企。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低质量学校会导致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被困在贫困的代际循环中。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不是这样的,以多伦多为例,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州政府资助的体面教育。虽然美国学校也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但主要还是依赖当地地产税,这就导致各地学校质量良莠不齐。当然,城市地区的富裕家庭可以绕过公立学校系统,直接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已然成为美国最深入的社会不公之一。
贫困社区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缺少好学校,因为那里的儿童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有利于学龄前儿童的发展,符合美国通过教育公共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众公共教育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教育的大幅扩张都刺激了经济发展,也推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26] 现在,增加对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在长期贫困社区的投资,也能提高社会整体人力资本和经济水平。
从根本上说,贫困就是缺钱。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最低工资或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负收入所得税”将部分税收返还给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方法比名目繁多的住房、食物、儿童支持等直接援助项目都更经济有效,也省了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
对基本收入保障项目的普遍批评是它会鼓励懒人,但负收入所得税则鼓励人们工作和创业,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政府的支持力度逐步降低。这一税收制度没有看起来那么激进,它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差点就被纳入美国税收政策中。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在实施了,还有很多国家在考虑实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自由派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最先提出了这一基本方法,很多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它的支持者。最近很多硅谷的企业家重提这一理念,认为这是打击贫困最有效的途径。 [27]
除了消除贫困,负收入所得税还有诸多益处。它为从事着养育子女、照顾生病亲人等零报酬工作的人提供了支付机制。承诺最低收入还能作为低成本原始资本,给创业阶段的人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日常生活。 [28]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五章提到的,这种收入重新分配机制最终能起到降低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利用负收入所得税、按当地生活水平调整的最低工资和上述其他方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城市化知识经济的不平等。然而我们要记住,新经济结构产生后,要经历一个漫长历程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与公共政策,消除新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平等,并创造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工业时代,这一过程从19世纪中期持续到20世纪中期,长达大半个世纪。旧社会安全网产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目的是解决旧工业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现在它已经无法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地域不平等和城市与郊区的集中贫困了。我们亟须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解决城市化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
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
虽然美国可能缺乏足够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有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来实施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然而,新城市危机并不止步于美国国界。在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城市化发展地区,超过10亿人口饱受其害,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还更加严峻。过去,美国的城市政策往往聚焦于国内,现在是时候使之国际化了。我的第六个提议就是,美国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在全世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打造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城市。
将综合的城市政策和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对美国益处良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建造中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发达城市能帮美国打开新的商业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不稳定地区建造强大和有弹性的城市,有助于实现重要的外交、军事和人道主义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和缓解迅速发酵的难民危机。
城市稳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世界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并减少暴力犯罪。实际上,全球恐怖主义滋生的衰败国家都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方。 [29] 军事干涉本身很容易摧毁大城市,并让人口更加分散,带来城市化水平和稳定水平双双降低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分裂地区建造稳定的城市能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美国还应考虑支持难民城市的发展,让它们更好地利用难民的才能。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如协助修建难民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全球难民危机更有效、成本更低,也能让难民如愿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 [30]
把美国的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的重点从“国家重建”转化为“城市重建”有很多好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造人口更密集、更清洁、能源利用率和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有利于降低贫困,加强全球稳定性,并创造更强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市长等城市领导者管理着全球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中心,与他们建立新型关系也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
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
我在写作本书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构想一个新型民主党政府,它将开展持续、深入的投资,以满足开启惠及全民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我的改造方案很彻底——将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扩张为更广泛的城市发展部,处理与城市地区有关的联邦提案;类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城市委员会”,为总统提供有关城市政策的建议;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联邦对城市的投资应该交到市长和当地官员手中,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本地经济和解决本地难题的人。
然而,事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逆转——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我所设想的蓝图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期间得以实现了。特朗普可能会兑现竞选承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很可能只是胡乱投资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不是对公共交通、能源利用效率和廉价住房进行战略性投资,而可持续和富有包容性的城市化发展需要的是后者。共和党多数派肯定会继续削减已经十分贫瘠的公共交通、廉价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联邦支出,当地政府、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肯定会忙得团团转来补上这些缺口。
如果特朗普真的兑现竞选承诺,在边境修墙,阻止移民入境,那么他将摧毁美国建国的基础——活力与多元化,把人才和创新推向别的国家。新城市危机带来的地理和文化分化十分深刻,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消弭的,而我们的新政府只会令它继续恶化。
在城市政策和投资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正努力将基建投资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以及开发有关经济适用房和城市发展的新战略(我和其他优秀的城市经济学家都被包含其中)。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政府新设立了城市和建筑环境部,负责在国家层面协调城市发展事宜。
然而,即便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权联邦政府期间,我们也能做出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赋予城市和社区更大的控制权,让它们发展自身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在这方面英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城市与国家政府建立了一种受到左右两派领导人支持的新型合作关系,包括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前工党领袖爱德华·米利班德,米利班德还曾提议建立一个“城市参议院”。2015年,由英国商业领袖、高级官员、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组成的蓝丝带委员会提出了增强城市权力的四个关键:将决策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变为城市;赋予城市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权力;让城市官员进入国家代表机构,并在内阁为他们保留永久席位;设立新机构来协调对城市地区基础设施、人才和经济发展的投资。 [31]
美国的市长和社区领导人现在应当积极争取权力,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因地制宜地解决本地问题,这种战略既能发挥本地创新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优势,也能适应各城市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其实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地理分化已经太严重了,可能很难就城市问题达成国家层面的共识,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通用方法,能解决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高昂的蓝州城市地区到人口较少、汽车依赖度更高的红州城市地区的各种问题。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需求差异极大,正如我们需要根据地区状况调整最低工资,制定城市政策时也应根据当地需求量体裁衣。以基础建设为例,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需要更多公共交通,而人口更稀少的地区需要更多道路和桥梁。因此赋予城市、郊区和社区更多自主权来处理它们各自的问题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建议。
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比党派活跃分子更务实。我在美国各地访问时,很难看出地方官员是共和党、民主党或是无党派独立人士,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是由当地实际需求驱动的,而不是由某种党派意识形态驱动的。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本地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也最有可能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的作者、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指出,要让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就应尽量减少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收缴的财政收入。 [32]
由两个党派的市长共同发起这一提议更容易在联邦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美国有极大的制度优势,灵活的联邦制能调整和平衡权力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的分配。罗斯福新政期间,罗斯福总统在联邦政府和市政府之间建立了新型合作关系,是时候再来一次了,但这次权力应向地方政府倾斜。
现在正是重塑城市治理、让地方官员能更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机。解决某些城市问题需要大范围合作,这些是目前分散的市政府系统无法提供的。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规模调整权力控制范围,例如,公交运输投资可以由一个都市圈里的各个城市和郊区,甚至一个大城市地区的各都市圈共同监督完成。
如果今天市长和地方官员抓住主动权,努力争取权力下放,那么当风向转变,美国准备再次投资重建城市和郊区时,他们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但当我想到未来的图景可能是这样时,言语已经无法描述我内心的惆怅:急需的经济适用房和交通系统不会建成,集中贫困的原因仍未解决,社会经济阶层固化。但我也记得在此前见证城市衰落和重生的大循环时所学到的,这不是我们的国家第一次背弃城市。不管在漫漫历史中发生过什么,城市仍然是最伟大的创新、经济增长、多样性、包容性和社会进步引擎,它们还将继续引领文明的前进方向。
新城市危机是历史性的分水岭,我们的应对方式将决定城市、郊区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个富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繁荣新时代,还是沦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分裂问题的牺牲品?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城市危机只会继续恶化。赢者通吃城市化进程中,赢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将继续扩大。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会变得昂贵至极,成为封闭的镀金社区,创新活力随之消失,维持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基本服务业人员也只能被迫离开;老工业城市的复兴之路十分艰难;“太阳地带”城市将继续自欺欺人,认为随意扩张就等于增长;郊区的经济越来越萧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社区继续缩减,国家进一步分化为富人的封闭飞地和大片的衰败城市与郊区;穷人和弱势群体将深陷日益扩大的经济与社会衰退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地区,将出现城市化水平提高而经济没有增长的怪象,超过10亿新城市居民将困于脏乱差的贫民窟并长期贫困。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城市危机这一当今时代的核心危机,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激发新一轮创新浪潮、创造充足的就业和经济机会,并且消除日益深化的经济鸿沟。
我对克服危机持谨慎而现实的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尽管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阻力重重,但城市仍是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工具。城市复兴带来了种种挑战,并且想对它们视而不见越来越难。20世纪的富人可以住在封闭的崭新郊区社区,乘空调火车或开车到守卫森严的办公楼上班,而现在所有的城市功能缺陷都一目了然。即使一些城市的部分区域已经被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占领了,但这些城市仍有丰富的种族和阶级多样性。市场、地方官员和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他们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
最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倒退。人在社会中的聚集推动了人类发展的每一步。现在“城市主导增长”的基本逻辑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然而,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的,在继续前进之前可能会倒退。新经济秩序出现后,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期,才能配套建立起稳定新秩序的制度与政策,并使更广泛人群从中获益。在我们上一个伟大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大型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最终,恢复经济繁荣的道路将取决于我们的城市和更优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
实现这种新型城市化是可能的,但它绝不会自动发生。我们是选择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分歧和矛盾,还是选择更全面、更公平的惠及全民城市化带来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和面临的斗争。
[1] Russell Berman, “Hillary Clinton’s Modest Infrastructure Proposal,” The Atlantic, December 1, 2015,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12/hillary-clintons-modest-infrastructure-proposal/418068; Paul Krugman,“Ideology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4, www.nytimes.com/2014/10/27/opinion/paul-krugman-ideology-and-investment.html; Ezra Klein,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2014,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4/01/14/larry-summers-on-why-the-economyis-broken-and-how-to-fix-it.
[2] 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的人口规模(0.61)和人口密度(0.55)正相关,也与密度的间接衡量指标——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口比例(0.42)正相关。它还与工资(0.50)、收入(0.34)和人均经济产出(0.34)正相关,与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度(0.61)、劳动力中创意阶层的占比(0.5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5)正相关。相反,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劳动力中蓝领阶层占比(-0.55)负相关。与不平等和隔离类似,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多元化的两个关键标志正相关——在国外出生的成年人比例(0.52)和同性恋人口比例(0.61)。另外,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地区的政治立场和投票模式也息息相关:它与城市地区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0.59)正相关(用2016年希拉里得票比例衡量),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0.55)负相关(用2016年特朗普得票比例衡量)。关于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完整排名,参见附录表4。
[3] 关于长期经济停滞的概念,参见Timothy Taylor, “Secular Stagnation:Back to Alvin Hansen,” Conversable Economist, December 12, 2013, http://conversableeconomist.blogspot.ca/2013/12/secular-stagnation-back-toalvin-hanson.html; Larry Summers,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49,no. 2 (2014): 65–73, http://larrysummer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NABE-speech-Lawrence-H.-Summers1.pdf。关于美国创新和更广泛的生产力下滑,参见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Krugman, “Ideology and Investment.”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July 12, 1893, 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 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 org/pds/gilded/empire/text1/turner.pd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1); Kenneth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Gerald Gamm and Thad Kousser, “No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Failure of Big-City Bills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1880–200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4 (2013): 663–678. 研究追踪了13个州立法机构从1881年到2000年的1700个与市或郡有关的立法,发现与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关的立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远低于与小地方有关的立案,并且小地方立法者提出的立案被通过的可能性是大城市立法者的两倍。
[7] Richard Florida, “Is Life Better in America’s Red States?,” New York Times,January 3, 2015, www.nytimes.com/2015/01/04/opinion/sunday/is-lifebetter-in-americas-red-states.html.
[8] Tyler Cowen, “Market Urbanism and Tax Incidence,” Marginal Revolution,April 19, 2016,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6/04/market-urbanism-and-tax-incidence.html.
[9] 引自Stephen Wickens, “Jane Jacobs: Honoured in the Breach,” Globe and Mail, May 6, 2011, www.theglobeandmail.com/arts/jane-jacobs-honoured-inthe-breach/article597904.
[10]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97 (1879)]. For more on George, see Edward T. O’Donnell,Henry George and the Crisi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Why Henry George Had a Point,” The Economist, April 1,2015, 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5/04/land-value-tax.
[11] David Schleicher, “City Unplanning,” Yale Law Journal 122, no. 7 (May 2013): 1670–1737.
[12] Enrico Moretti and Chang-Tai Hsieh, “Why Do Cities Matter? Local Growth and Aggregate Growth,” April 2015,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chang tai.hsieh/research/growth.pdf.
[13] Richard Florida, “The Mega-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ch 11,2014,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mega-regions-of-north-america.
[14] 这些时长估计来自 Richard Florida, “Mega-Regions and High-Speed Rail,”May 4, 2009,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national/archive/2009/05/mega-regions-and-high-speed-rail/17006。
[15] Todd Sinai and Joseph Gyourko, “The (Un)Changin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Tax Benefits, 1980 to 200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3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 2004, www.nber.org/papers/w10322.pdf; Robert Collinson, Ingrid Gould Ellen, and Jens Ludwig,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07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071;Richard Florida, “The U.S. Spends Far More on Homeowner Subsidies Than It Does on Affordable Housing,” CityLab, April 17,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4/the-us-spends-far-more-on-homeowner-subsidies-than-itdoes-on-affordable-housing/390666.
[16] Richard Florida, “How the Crash Will Reshape America,” The Atlantic,March 2009,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9/03/how-thecrash-will-reshape-america/307293; Richard Florida, The Great Reset: How the Post-Crash Economy Will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 (New York:Harper Business, 2010); Nick Timiraos, “U.S. Homeownership Rate Falls to 20-Year Low,”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9, 2015, http://blogs.wsj.com/economics/2015/01/29/u-s-homeownership-rate-falls-to-20-year-low.
[17] 关于租房数量上升和下文中租房负担上升的数据均来自哈佛大学房屋研究联合中心,参见America’s Rental Housing: Expanding Options for Diverse and Growing Demand,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December 2015, www.jchs.harvard.edu/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s-rental-housing-expanding-options-diverse-and-growing-demand。
[18] Richard Florida, “The Steady Rise of Renting,” CityLab, February 16, 2016,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2/the-rise-of-renting-in-the-us/462948.
[19] Miriam Zuk and Karen Chappel, “Housing Production, Filtering, and Displacement: U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Research Brief, May 2016, www.urban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udp_research_brief_052316.pdf.
[20] Arindrajit Dube, “The Minimum We Can Do,”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1/30/the-minimumwe-can-do; Arindrajit Dube, T. 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no. 4 (2010): 945–964.
[21] Richard Florida, “The Case for a Local Minimum Wage,” CityLab,December 11, 2013, www.citylab.com/work/2013/12/why-every-city-needsits-own-minimum-wage/7801; Arindrajit Dube, “Proposal 13: Designing Thoughtful Minimum Wage Policy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4/06/19-minimumwage-policy-state-local-levels-dube.
[22] James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3] Zeynep Ton, The Good Jobs Strategy: How the Smartest Companies Invest in Employees to Lower Costs and Boost Prof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Richard Florida, “The Business Case for Paying Service Workers More,” CityLab, March 3, 2014, 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4/03/case-paying-service-workers-more/8506.
[24] Michael Erard, “Creative Capital? In the City of Ideas, the People with Ideas Are the Ones with Day Jobs,” Austin Chronicle, February 28, 2003 www.austinchronicle.com/news/2003-02-28/147078.
[25]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26] 关于儿童早教,参见James J. Heckman,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 (June 2006): 1900–1902;William Dickens, Isabell Sawhill, and Jeffrey Tebbs, “The Effects of Investing in Early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6;Timothy Bartik, “Investing in Kids: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pjohn Institute, 2014, http://research.upjohn.org/up_press/207。关于公共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参见 Robert A. Moffit,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and the Evolution of U.S.Welfar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no. 1 (August 2003):119–140。
[28] 一位评论家称之为人的风险投资。Steven Randy Waldman, “VC for the People,” Interfluidity, April 16, 2014, www.interfluidity.com/v2/5066.html.
[29] Richard Florida, “How Stronger Cities Could Help Fix Fragile Nations,”CityLab, November 19,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11/howstronger-cities-could-help-fix-fragile-nations/416661.
[30] Brandon Fuller, “Rethinking Refugee Camp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Solving an Intractable Problem,” City Journal, December 11, 2015, www.city-journal.org/2015/eon1211bf.html.
[31]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Unleashing Metro Growth: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ity Growth Commission,” London, October 2015, www.thersa.org/discover/publicationsand-articles/reports/unleashing-metro-growth-final-recommendations.
[32] 参见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Cites, Rising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arber, “Can Cities Counter the Power of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he Nation, November 14, 2013, www.thenation.com/article/can-cities-counter-the-power-of-president-electdonald-trump/。
本附录提供了有关本书使用的主要变量和统计分析的详细信息,以及美国城市在以下三个主要指数上的完整排名:新城市危机指数、隔离-不平等指数和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主要指标和测量方式
关键变量和指数的定义和来源如下。
阶层
创意阶层。 创意阶层包括从事以下工作的人群: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建筑和工程,生命、自然和社会科学,艺术、设计、音乐、娱乐、体育和媒体,管理、商业和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和培训。
工人阶层。 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以下蓝领工作的人群:工厂生产,开采、安装、维护和修理,生产、交通和物流,建筑。
服务阶层。 服务阶层包括从事以下日常服务工作的人群:食品准备等食品服务,建筑和场地的清洁维护,个人护理和服务,低端销售,办公室和行政支持,社区和社会服务,安保服务。
三类阶层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0年。
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是基于基尼系数的传统衡量标准,来自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
工资不平等 :工资不平等反映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之间的工资差距,基于泰尔指数计算,该指数是衡量工资不平等的常用指标。 [1] 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0年。
综合不平等指数 :该指数是用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得到的平均加权指数。
经济隔离
第六章中用到了两类经济隔离的衡量标准。
特定经济隔离指数
特定经济隔离指数有七个,它们反映了美国城市中七万多个人口普查区的隔离情况。每个指数都是根据相异指数计算的,该指数比较某地区特定人群与其他人的分布情况。 [2] 特定人群与整体人口相比,分布越均匀,隔离程度就越低。相异指数D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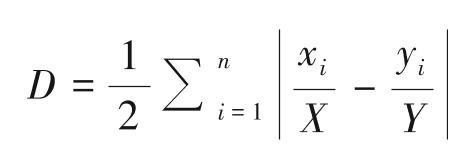
x i 是第i 个人口普查区中特定人群的人数,X 是大城市地区中特定人群的人数。y i 指人口普查区中“其他人”的数量,Y 是大都市区中“其他人”的数量。n 表示大城市地区中人口普查区的数量,D 表示我们选定的特定群体在各人口普查区的分布与其他人的分布差异。D 的数值范围从0到1,其中0表示最低隔离(或完全融合),1表示最高隔离。这个指数是隔离的绝对量度值,数值越高表示隔离程度越高。反映各个群体的住宅位置的数据来自2010年的美国社区调查。
穷人的隔离 :衡量收入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水平的家庭的居住隔离。
富人的隔离 :衡量收入高于20万美元的家庭的居住隔离。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隔离 :衡量未获得高中学历的成年人的居住隔离。
大学毕业生的隔离 :衡量大学毕业的成年人的居住隔离。
创意阶层隔离 :衡量创意阶层的居住隔离。
服务阶层隔离 :衡量服务阶层的居住隔离。
工人阶层隔离 :衡量工人阶层的居住隔离。
综合隔离指数
还有四个综合指数衡量更广泛的经济隔离,是相对的衡量标准,数值较高表示与其他城市相比经济隔离程度较高。
收入隔离 :综合富人隔离和穷人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教育隔离 :综合大学毕业生的隔离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未完成高中的人)的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职业隔离 :综合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的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综合七个特定经济隔离指数(同比重加权)的经济隔离指数。
其他综合指数
有两个更广泛的综合指数,也是相对的测量标准,数值较高表示与其他城市相比程度较高。
隔离-不平等指数 :将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工资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数据以相同比重加权结合,得到的衡量不平等和隔离水平的综合指标。
新城市危机指数 :将工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住房负担(基于住房成本与收入的比值)四项指标以相同比重加权结合,得到的综合指标。
其他变量
书中统计分析使用的其他关键变量如下。
人均收入 :平均人均收入,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工资 :平均工资,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人均经济产出 :基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大学毕业生 :大学本科以上成年人口的比例,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高科技产业 :基于米尔肯研究所的技术极点指数,该指数衡量单个城市高科技产业产出占国家总高科技产业产出的比值 [3] ,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的郡商业模式报告。
特定创意阶层职业 :将创意阶层职业分解为特定的亚群组,包括科学和技术,商业和管理,艺术、文化和媒体,教育和医疗。
风险资本投资 :投资于高科技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金额,来自汤森路透2013年的分析报告。
工会化 :工会成员在工人中的占比。 [4]
住房成本中位数 :月住房成本的中位数,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住房成本占收入的比例 :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密度 :基于到市中心或市政厅距离的人口加权密度,来自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5]
公共交通 :乘公共交通工具通勤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独自驾车上班 :独自驾车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骑自行车上班 :骑自行车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步行上班 :步行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种族和民族 :白人、黑人、亚洲人或拉丁裔人口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外国出生居民 :外国出生居民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男女同性恋指数 :衡量男女同性恋家庭聚集的区位指数,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自由派或保守派 :根据2008年、2012年和2016年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在各个州和城市获得的选票。 [6]
附表1 风险投资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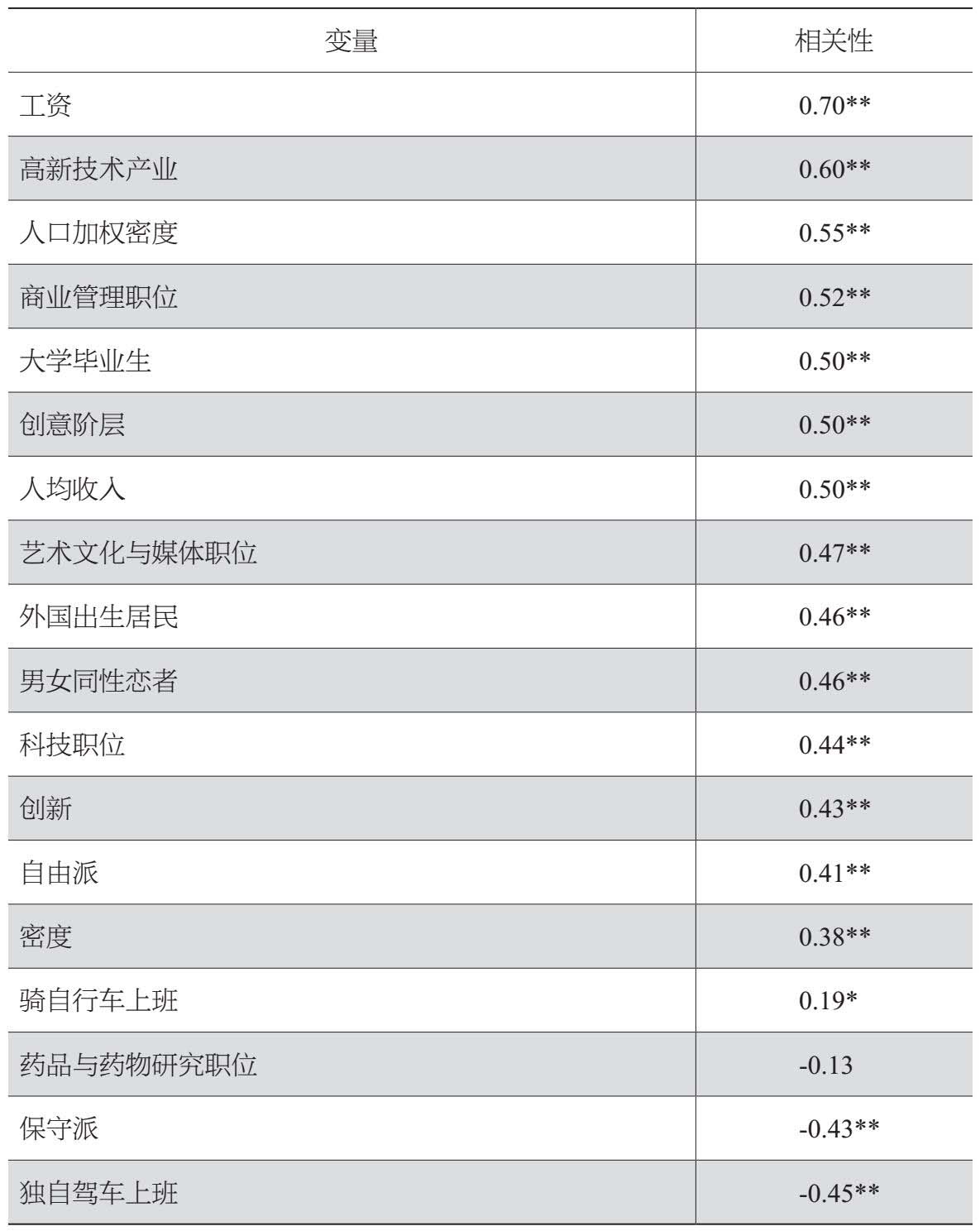
资料来源:分析来自夏洛塔·梅兰德,基于汤森路透、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注:一个星号表示统计数据的显著性在5%的置信区间,两个星号表示统计数据的显著性在1%的置信区间。
附表2 绅士化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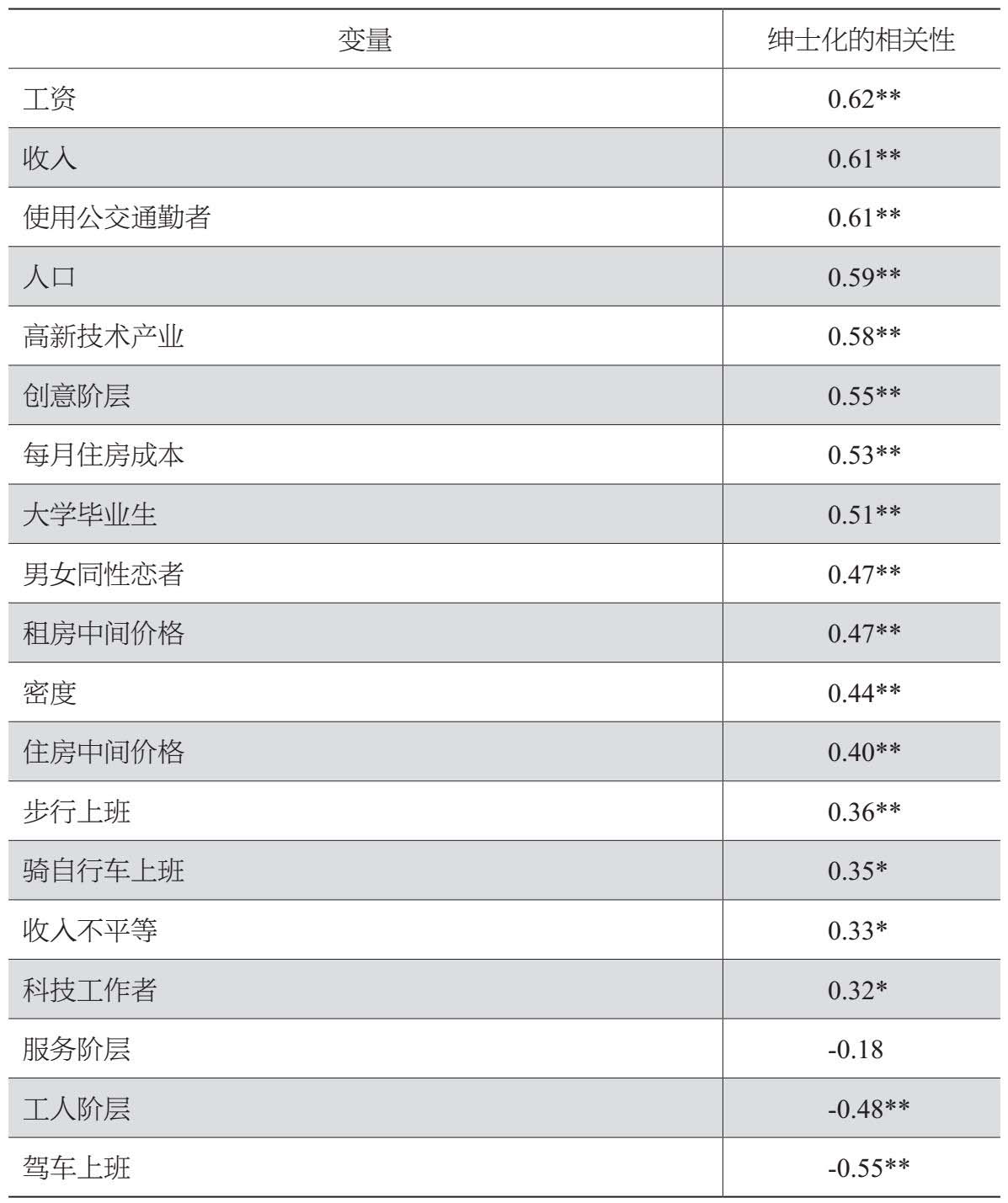
资料来源:分析来自夏洛塔·梅兰德,数据来源于丹尼尔·哈特利的《绅士化与金融健康》,以及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注:绅士化是指2000年至2007年间,从大城市地区房价分布的下半部分向上半部分转移的社区或人口普查区域。
附表3 经济隔离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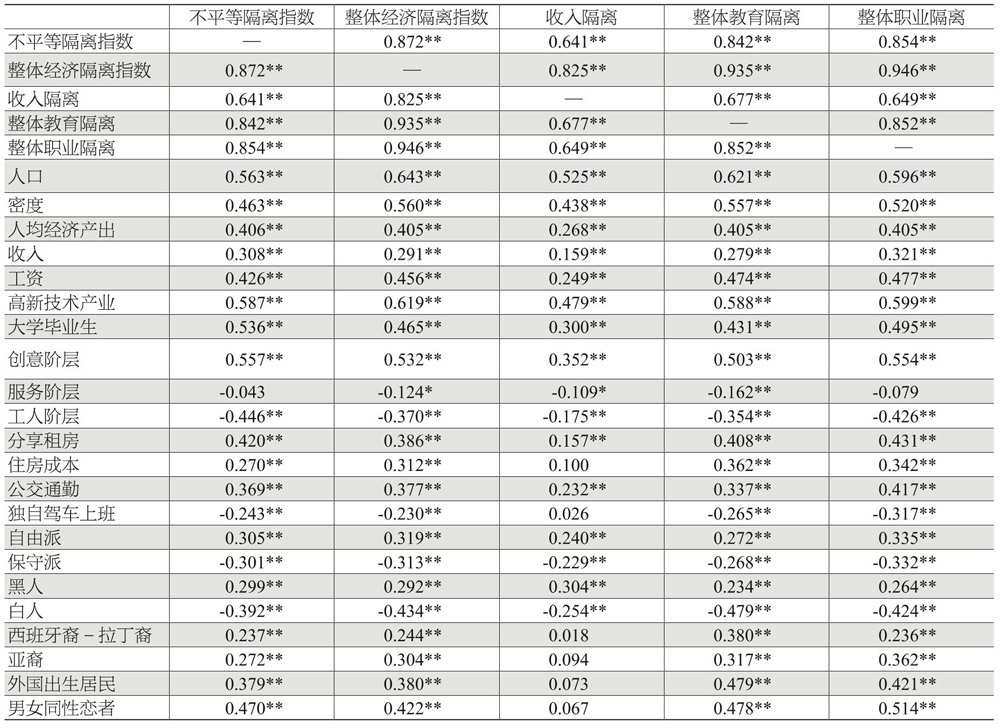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文本中的主要指标和测量方式。
附表4 大都会地区在新城市危机指数、不平等隔离指数、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上的排名

续表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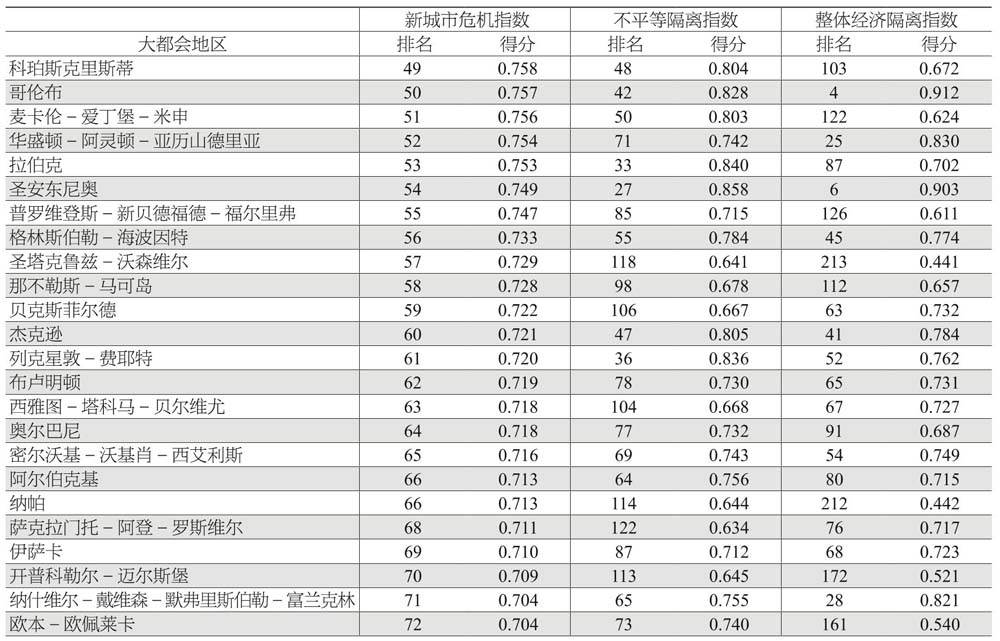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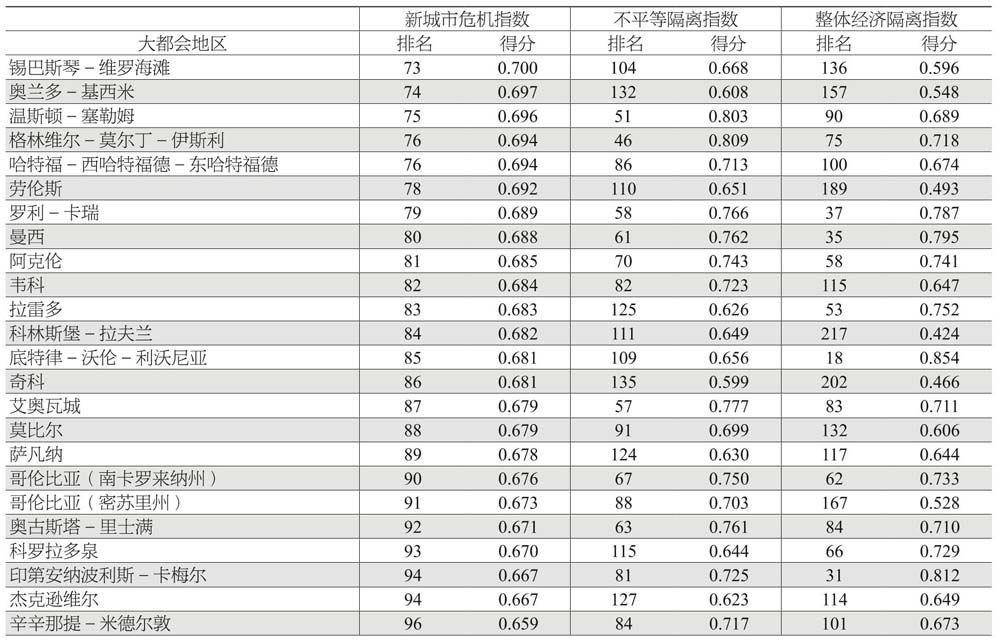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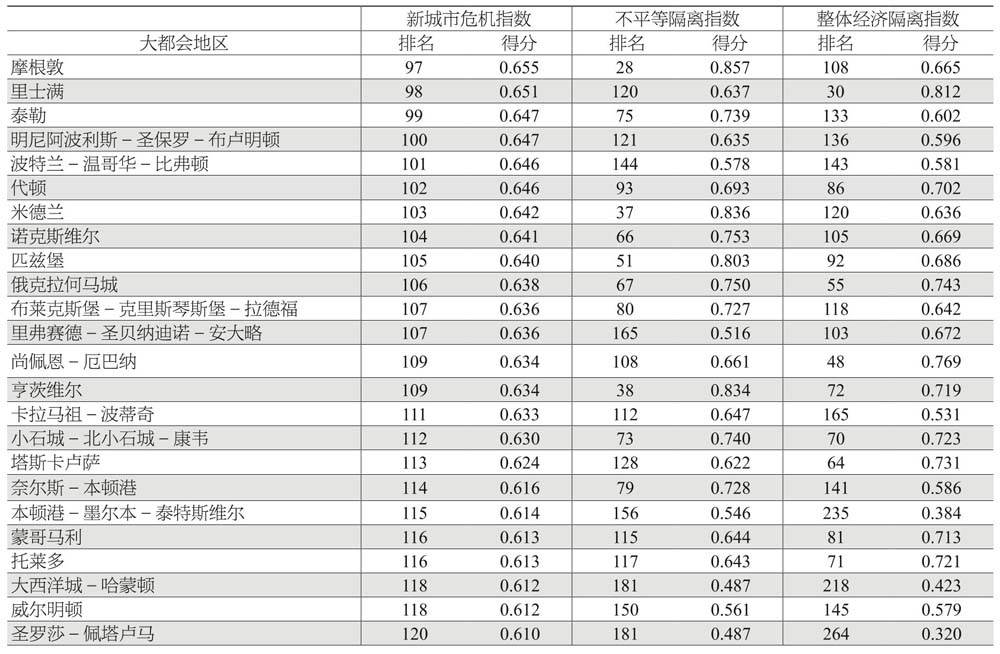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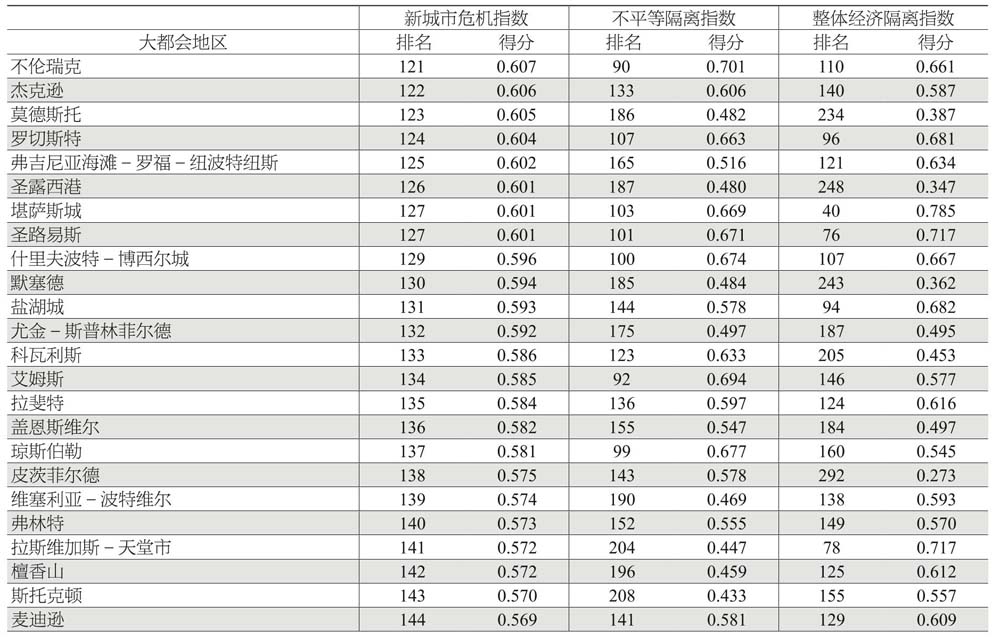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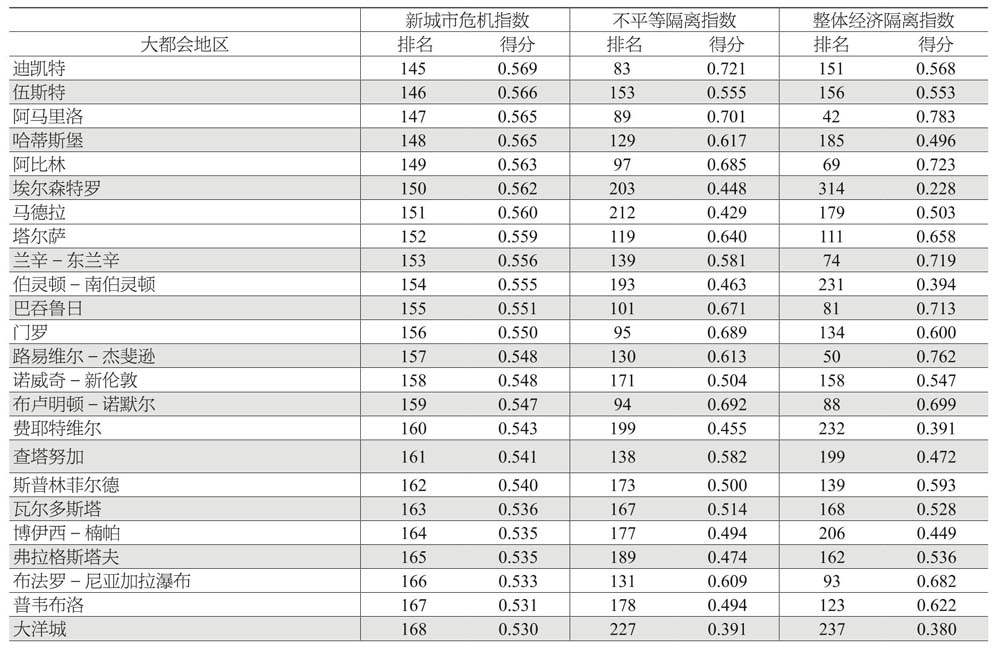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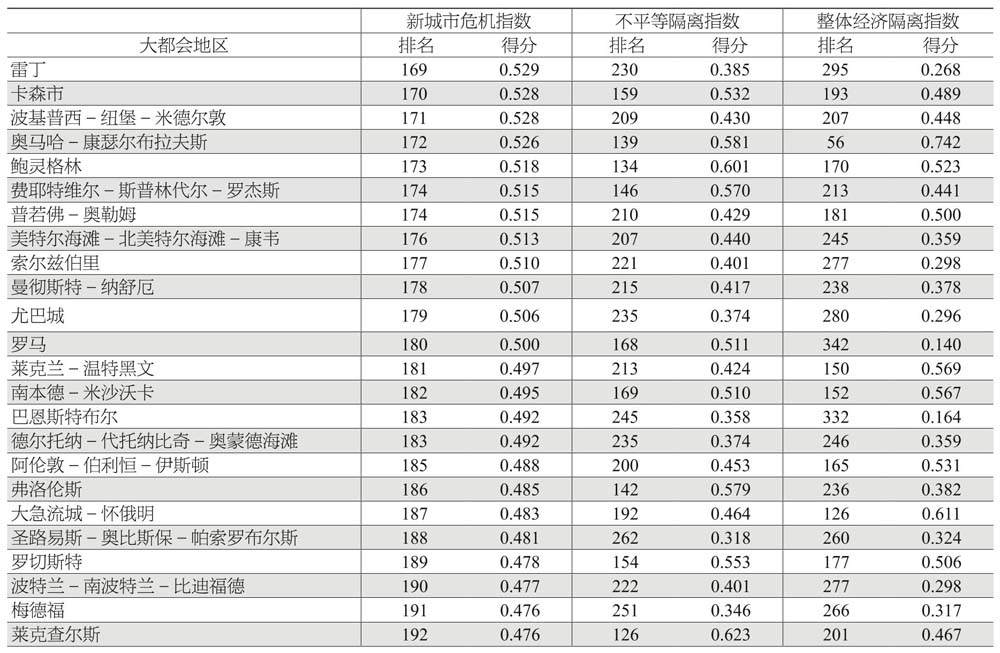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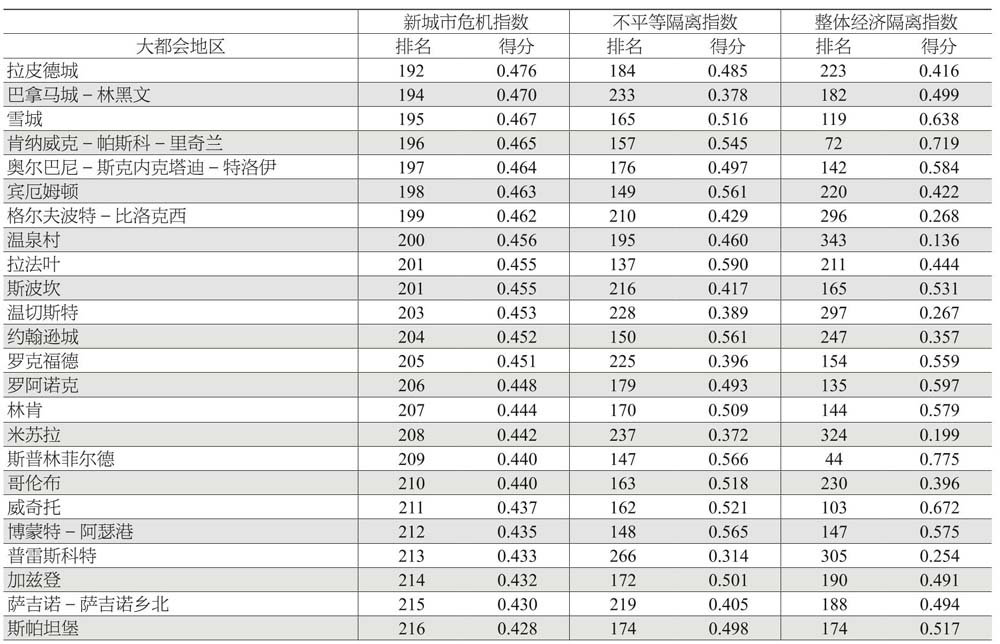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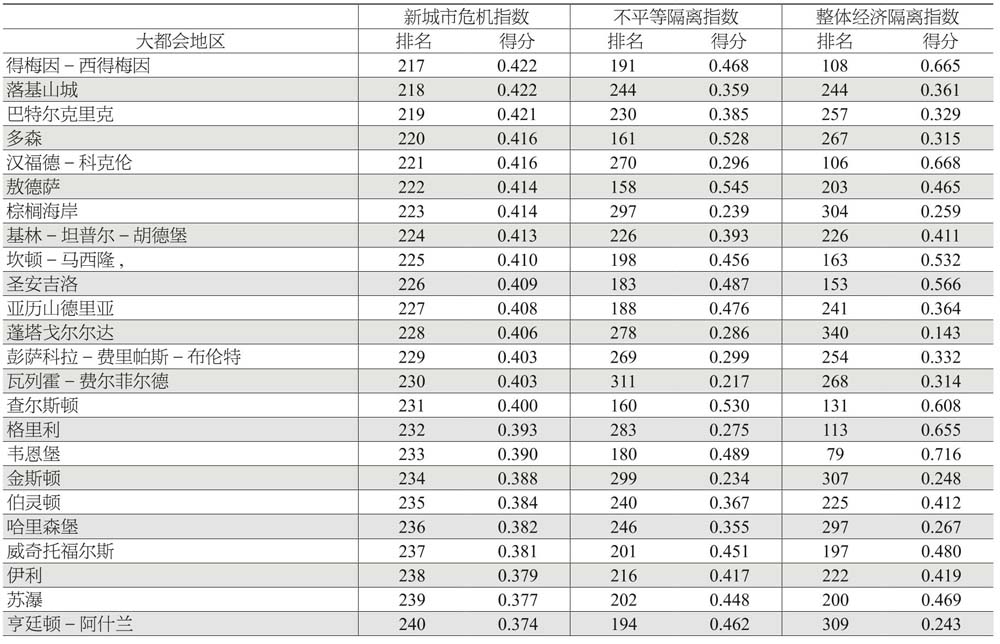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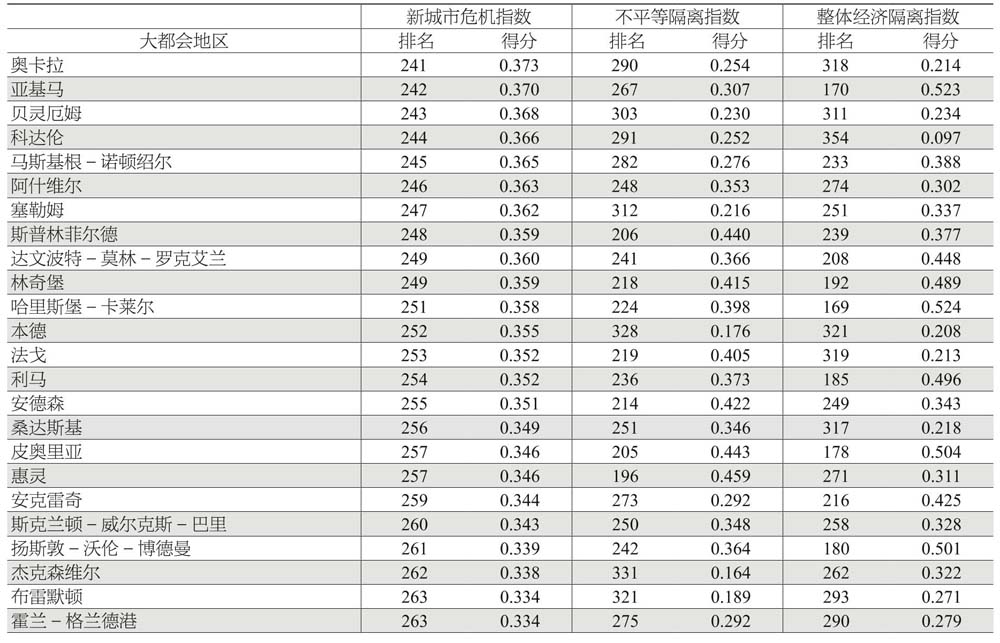
续表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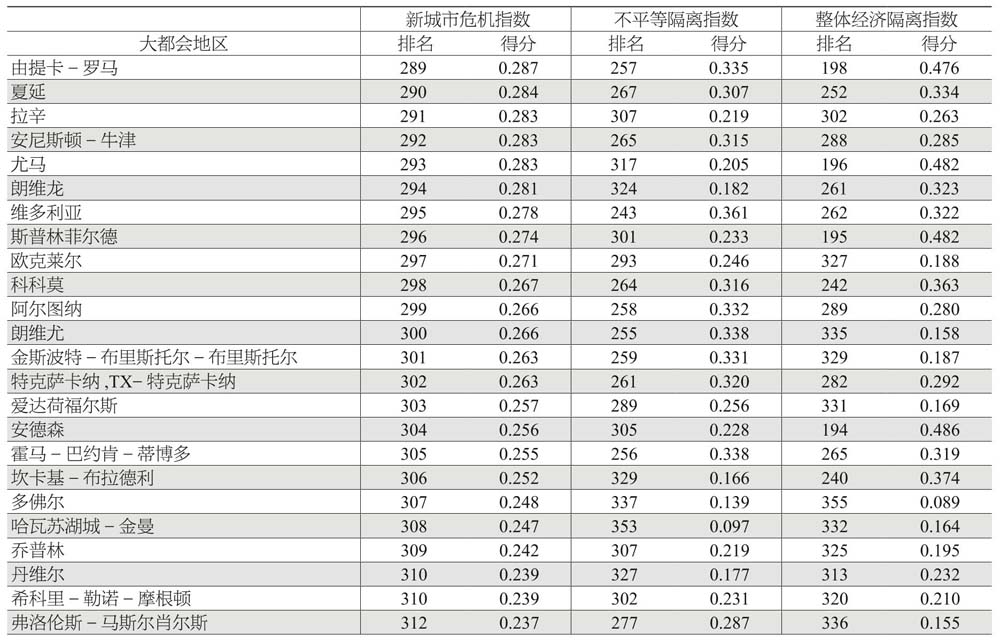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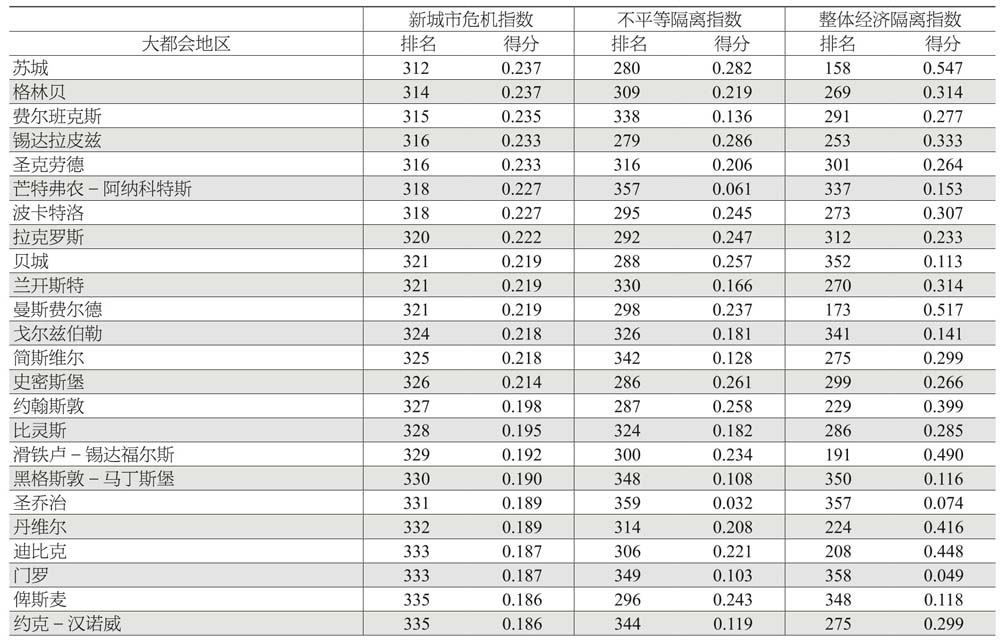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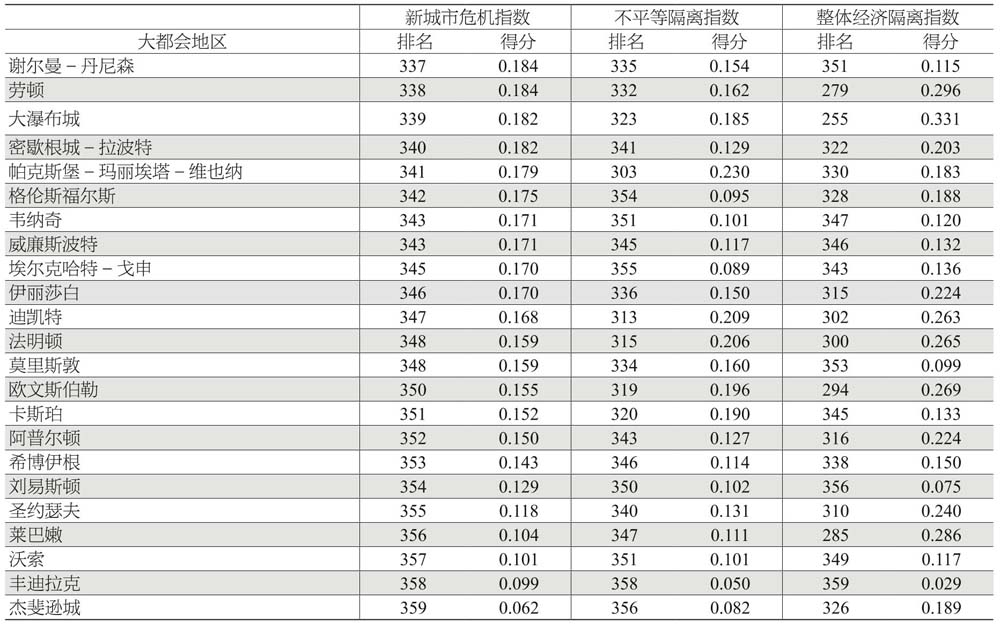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人口调查局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1] Paul D. Allison, “Measures of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no. 6 (December 1978): 865-880.
[2] 关于相异指数,请参见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67, no. 2 (1988): 281–315。
[3] 关于米尔肯研究院的高科技指数,请参见Ross DeVol, Perry Wong, John Catapano, and Greg Robitshek, America’s High-Tech Economy: Growth,Development, and Risks for Metropolitan Areas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1999)。
[4] Barry Hirsch and David MacPherson, “Union Membership and Coverage Database from the CPS,” Union Stats, 2014, http://unionstats.com.
[5] 关于人口加权密度,请参见Steven G. Wilson, David A. Plane, Paul J.Mackun, Thomas R. Fischetti, and Justyna Goworowska et al.,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and Micropolitan Population Change: 2000 to 2010, 2010 Census Special Reports, September2012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www.census.gov/prod/cen2010/reports/c2010sr-01.pdf。
[6] 州级选举数据来自权威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城市的选举结果由郡县结果汇集而成,参见Dave Leip’s “Atlas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or 2012 and 2016, http://us electionatlas.org。
我关于这本书的想法是受到一场谈话的启发。2013年夏天,我在纽约和编辑与出版商探讨关于另一本书的构想。那是一个天气宜人的夜晚,我在苏荷区克罗斯比街酒店的休息室与Basic Books(出版社)的人聊天,在我努力解释自己观察到的再城市化趋势时,出版商拉腊·海默特打断了我:“你说的是新城市危机,写这本书吧。”她确实是对的,在我还几乎不确定它是什么时,就已经忙着在做这件事了。
但首先,我需要重新调整自己。我最早的研究方向是住房和城市问题,但在职业生涯后面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专注于研究促进城市创新及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本书中我需要深入探讨城市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城市贫困、集中劣势和社区的长期影响。我与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马丁繁荣研究所的团队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的地理分布、绅士化的猜想与现实、亿万富翁的地理分布和超级富豪的城市入侵、创业城市化的规模和挑战、城市和郊区之间新的深层鸿沟,以及全球城市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研究新城市危机的深度以及绘制它在城市、郊区和全部都会区的断层线时,我发现不论是城市经济学还是城市社会学都没能勾勒出它的全景。前者主要关注集中优势,后者主要关注集中劣势,把二者观点结合互补,就能找到一个理解新城市危机的新方式和综合体。
这个大型项目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从中收获了诸多启发和教益。对作者而言,海默特是最理想的出版商。她帮我打磨观点,不断激励和敦促我,并和我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让我能尽量清晰和直接地表达观点。我的经纪人吉姆·莱文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坚持伴它度过各个成长阶段,并最终帮它找到了完美的归宿。
亚瑟·戈德瓦格是个智多星,也是最优秀的作家和编辑之一。他是我的绝佳参谋,总能使我的写作更清晰明了。夏洛塔·梅兰德是位统计学家,负责搭建本书中的关键指标和统计分析。出版社的布莱恩·迪斯特尔伯格的编辑保证本书内容紧凑、紧扣重点,凯西·斯特雷克弗斯对本书进行了仔细审稿,梅丽莎·韦罗内西高效完成了本书的最终制作。
我特别感谢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包括那些已经离开研究所去追求更伟大事业的人,他们的研究给本书奠定了基础。凯伦·金作为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与组织从数据分析到地图、图表和表格的编辑、引用和构建的所有工作;伊莎贝尔·里奇和泰勒·布莱克负责制作地图并辅以数据分析;米歇尔·霍普古德负责整理图表;金·西尔克和伊恩·高梅利汇总源材料和参考资料;帕特里克·阿德勒、泰勒·布里奇斯和扎拉·马西森合作完成《拼布城市》那一章中的原始地图与分析。
马丁繁荣研究所是一个很棒的研究所,我来罗特曼学院就是因为罗杰·马丁。执行董事贾米森·斯蒂夫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瓦什·贝德纳是城市问题方面的关键人物,他负责维持项目正常运转、管理预算和建立团队文化;瓦莱里娅·斯拉多耶维奇-索拉和奎恩·戴维森负责研究所的日常运作;已故的乔·罗特曼和罗特曼家族为研究所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我在纽约大学城市实验室的同事史蒂文·佩德戈也是CCG(Creative Class Group)咨询公司的研究董事,他使我不断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专业实践,帮我更加深入地理解本书讨论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意义。CCG的拉赫曼·亚历山大高效支持我的各项活动,无论我走得多远,她都能保证我坚持下去按时完成工作。
过去几年,我在《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朋友阿利亚·本迪克斯、斯蒂芬妮·加洛克、萨拉·乔纳森、阿里安·马歇尔和安德鲁·斯莫尔协助我研究和发表在CityLab(城市实验室)网站上的帖子,其中许多帖子都成了某项新研究的起点,我后来又对它们进行了充实和拓展。
我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同事马克·罗森伯格和布莱恩·施里纳在迈阿密海滩城市工作室给我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工作室,在加拿大寒冷的冬休期我能去那里思考和写作。
还有很多人对本书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们,包括帕特里克·阿德勒、路易斯·贝当古、博伊德·科恩、吉姆-麦·卡特勒、扬·德林、梅勒妮·法斯克、约瑟·洛沃、罗伯特·曼杜卡、加布·梅特卡夫、塞斯·品克斯、亚伦·勒恩、乔纳森·罗思韦尔、罗伯·桑普森、帕特·夏基、丹·西尔弗、格雷格·斯潘塞和莱曼·斯通。
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个大家庭,它给予我宽慰和快乐。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拉娜,她是真正的自然之力,帮我打磨想法,告诉我它们听起来是否正确。她还照管我们的生意和生活琐事,让我能专注于研究项目。我的至爱用她无限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情丰富了我的每一天。我想把本书献给我们家庭的新成员,米拉·西蒙娜·佛罗里达。

谨以此书献给
朱利安、塞莱斯汀、拉克、安德鲁、瑞安、詹姆斯、约翰、玛丽和威尔,愿你们拥有一个更加公平、更少绝望的世界。
经济学家应该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教授及其杰作并不陌生,如其于2013年出版的畅销书《逃离不平等》。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注意迪顿教授的研究,这主要源于他在经济学顶刊发表的几篇关于健康与收入分配的必读论文。事实上,他的长期研究系统性地推进了人们对于贫困、健康、消费与发展经济学的认知,为人们深刻了解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也因此,他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9年,迪顿教授与夫人(也是同事)安妮·凯斯教授出版了一本新书,中文版叫《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是一本非常值得花时间细读的佳作,也是我近来难得一口气读完的新书。
该书所论主题相当复杂,有些主题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当下。然而,作者勇于直面诸多尖锐问题,运用超凡的驾驭能力,逐一道出精彩见解,其中不乏颠覆常人直觉的观点,让人脑洞大开。平心而论,这些观点若不是出自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力作,我未必会反思自己很多与书中观点相悖的看法。当然,我也未“照单全收”这本书中的所有结论。
在论及正文之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令人敬佩的谦卑态度和科学精神。在这本书中,他们始终把大众读者视为首要尊重的对象。在他们挥洒自如的笔下,尽管论述的是人类大是大非的问题,很多涉及学术性很强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医学相关命题,字里行间无不呈现他们对非专业读者进行的精心裁剪和深入浅出的耐心安排,漂亮的叙事文风更让人爱不释手。与此同时,他们对所论问题的严谨态度并未打折,与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无二致。针对关键的史料、数据、方法以及相关发现,他们要么给出自己坚信的肯定答案,要么向读者坦承他们的认知局限或明示结论的不确定性。
如果要全面领会《美国怎么了》的深刻内涵,不妨先浏览一下《逃离不平等》一书。《逃离不平等》是一部关于工业文明如何促进人类经济繁荣的巨著,基于大量的史料实证数据,全景式地展示了250年以来,得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人类总体上首次成功逃离了有史以来长期遭受的极度贫困与过早死亡的“马尔萨斯陷阱”。与此同时,因为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差异,贫富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不少。
《美国怎么了》的视角和论点则迥然不同,可以说是以揭示《逃离不平等》成功故事背后的负面问题为主线,展开了对美国在新世纪出现的社会“逆繁荣”现象进行的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用他们的话说,这本书的主题“没有那么令人振奋。它记录了绝望和死亡,批评了资本主义的多个方面,并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今日美国是否卓有成效提出了质疑”。
《美国怎么了》开门见山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当下逆繁荣变化的悲观图景。基于对美国历年死亡记录的精心分析,两位作者发现了令人吃惊而又沮丧的社会逆转现象,他们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流行病。自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的30年,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占了工作人群的38%,他们的命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成为因绝望而死亡的最大牺牲品,且人数不断增长。导致“绝望的死亡”的三大“杀手”分别是滥用阿片类药物中毒、酒精中毒的肝病以及自杀。而在同一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并未经历如此遭遇,尽管同期的期望寿命增长显著低于战后数十年的“黄金”时光。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黑人,虽然其绝对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平均寿命增长也几乎停滞,但没接受大学教育的黑人队列在同期并未出现“绝望的死亡”流行病抬头的恶劣趋势。
两位作者随后用大量篇幅讨论“绝望的死亡”之因。我最为欣赏的是其论证的“靶向”方法学。以第十章为例,题为“歧途:贫困、收入与经济大衰退”。凭直觉,我猜想这十有八九是所论问题的“元凶”——靶点。然而,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他们图文并茂地逐一予以“毙”之。说到贫困,他们证明了在过去30年,白人劳工的“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的蔓延与美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并不相关,所以主因一定不是他们比其他群体更穷。关于收入不平等,人们可能猜想其也是罪魁祸首。然而,他们认为,绝望的陷阱并非因为最顶尖的1%富人变得更富,而是因为绝望的人群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发生了灾难性退步,致使其收入、工作、家庭、婚姻状况全面崩溃。同理,他们基于1929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的数据分析,并未发现其间“绝望的死亡”人数激增,因此认为“剑指经济危机”也是认知歧途。他们还补充了国别比较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欧洲国家同期也经历了经济衰退、政策紧缩和高失业,然而都未曾发生类似的“绝望的死亡”流行病。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也没有回避一个颇为尖锐的说法:遭受“绝望的死亡”流行病侵害的一代人,也许是自身“丧失了勤奋精神”而懒得努力工作与积极上进的后果。对此,他们不以为然,并运用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原理争辩:如果是因为劳动力供方不务正业的行为,就业下降应该伴随市场工资上升才对,可实际数据显示的却是二者双降,所以最有可能是劳动力市场需方的萎缩所致。
拜读至此,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究竟能解密什么惊人答案。从微观的角度看,两位作者明确认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危机是造成没落和绝望的最直接原因”。这里,如同大多批评美国医疗体制的典型说法,他们也集中痛斥美国医疗的最大“表征”:一方面,支出了占GDP(国内生产总值)18%的巨额医疗费用,全球之最;另一方面,又未取得相应最好的健康结果,其惊人的浪费和低效似乎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巨大的医疗负担还“正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绝望的死亡”。但这并非重点,两位作者真正的重点是——美国医疗体制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的医药、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供给侧隐形“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牟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对为员工购买医保的雇主而言,不得不通过降低人员工资转嫁成本;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而言,情况自然更糟。再从宏观层面分析,两位作者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的制度缺陷。他们辩称,主要因为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为资本主义缔造繁荣的市场竞争难以奏效,进而不可能为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提供双赢结果。
如要解决美国医疗的上述重大问题,路在何方?两位作者坦承,他们无意也无力在这本书中绘制美好的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蓝图,但仍然尝试给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他们特别强调二次收入分配和建立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美国目前的税收制度需要改革,使其为全民提供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而不是当下的“劫贫济富”。不过,他们也再三声称,明确不赞成优先考虑对收入顶端的所有富豪课以重税来“劫富济贫”。这里,他们特别强调了区别“不平等”和“不公平”的重要性,前者包含了合法收入的差距,后者则是不义之财的结果。所以,公共税收政策的改革应该着力于如何“限制寻租和减少掠夺”,而“不必对被普遍认为公平收入的那一部分收入和财富征收高额税赋”。他们不无哲理地比喻道:“阻止小偷的正确方法是不让他们偷窃,而不是给他们加税。”
至于如何才能成功改革美国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及其医疗体制,两位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证,我想也不该做更多苛求。客观而言,这既非这本书的篇幅所能涵盖的内容,也不是仅凭两位作者就能完成的重任。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曾经说“医改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此话真的一点儿也不夸张。关注各国医改的读者朋友也许知道,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哪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堪称典范,足以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模式。事实上,医疗制度何去何从正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取向的重大议题,也是各国争论不休的热点、焦点问题。
在此,请容我对此书的结论要点从不同的视角谈三点个人之见。
第一,关于医疗市场的竞争问题。在国际医改和健康经济学文献中,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教授关于医疗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一般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医疗市场竞争效应的实证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正面、负面的都有,但据我所知,竞争有利于促进服务效率、医疗质量甚至成本管理的实证文献仍是主流。哈佛大学商学院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甚至声称,美国医疗问题的症结非但不是竞争本身或过度,而恰恰是缺乏有效竞争所致。
第二,关于医疗费用增长问题。对此,我特别赞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卡特勒强调的一个观点:医改经济学分析不该以控制医疗费用上涨为目的,而应聚焦于分析每一美元医疗开支的健康回报是否值得。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也曾在相关论著中独立提出了高度一致的见解。基于这个逻辑,国家医改的要务之一应是加强对医药技术和临床服务开展系统的经济学成本效益评价,从而不断完善医保目录和支付手段。事实上,各国近年来的确也正在此方面不断推进相关工作,包括中国的全民医保近期开展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以及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和美国临床与经济评价研究所(ICER)等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制度。众所周知,欧洲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伴随了强烈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社会保障色彩,美国长期践行的则更是以捍卫“个人选择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共政策。因此,如要推行更为彻底的社会保障和全民医保制度,必定要求美国民众放弃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资源支配权,从而让位于政府扮演更大的资源配置角色。对于美国人而言,此举非同小可,而是大是大非问题,更不是总统、政府、国会说了就能算事。想想看,历经多少前任总统的医改尝试失败之后,奥巴马总统好不容易成功通过了美国全民医保法案,也还险些因此被控为有悖美国自由精神的“违宪”之举而被弹劾。虽然逃过此劫,但特朗普上台后,仍旧以同样理由继续着推翻该法案的努力。目前来看,美国全民医保的命运仍然堪忧。即使两位作者也在这本书的结尾章节告诫,“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政府的危险,更大的政府意味着更多的寻租空间和更大的不平等”。他们坦言,曾经考虑以“资本主义的失败”为部分副书名,但最终选择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表达其希望拥有的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只是我的几点浅见,既不全面,更谈不上正确与否,就当抛砖引玉吧。最后,我还想与青年读者啰唆两句如何更好地阅读这本书的体会。这本书既涉及很多政治性很强的议题,又不乏学术性很深的研究问题。因此,我会尽量学习两位作者的治学精神,对于书中呈现的争议性、冲击性很强的观点结论,无论我们同意与否,接受还是弃之,只要坚持开放性、批判性的思维态度,相信也会受益匪浅。无论如何,我相信大多读者不会后悔阅读此书。
刘国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副主任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2013年出版的《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安格斯·迪顿讲述了一个乐观的故事。那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过去250年中人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描绘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进步,贫穷匮乏得到消减,人类寿命也不断延长。人类不断创造知识并对其加以应用,使这种进步成为可能。在这一进程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资本主义,它挟全球化威力之勇,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赤贫状态。民主不断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参与社会进步,投身于建设自己所在的社区和社会。
本书的主题则没有那么令人振奋。它记录了绝望和死亡,批评了资本主义的多个方面,并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今日美国是否卓有成效提出了质疑。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乐观,我们依然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加以管理实现普遍利益。世界不必像今日美国那样运作,而是应该将其重新定向,使其服务于大众的利益。自由市场竞争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它也在很多领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在提供医疗保障方面,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对美国人的健康和福祉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各级政府不愿像其他富裕国家已经实行的那样,推行强制医疗保险和强力控制费用,那么悲剧将不可避免。绝望的死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也只有美国——未能吸取这一教训的结果。
此前,资本主义也曾失信于大多数人,例如在19世纪初开始的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其后的大萧条年代。但最终,资本主义这头野兽被驯服,而非被杀死,并取得了《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所描述的巨大成就。如果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就可以确保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是另一场重大灾难的序幕,而只是暂时的挫折,未来我们将重新走上经济欣欣向荣、人民身体健康的康庄大道。我们希望本书虽然不能像《逃离不平等》那样鼓舞人心,但可以帮助我们重回正轨,在21世纪能够重现过去取得的进步。世界的未来应该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是绝望的未来。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之时无须频频查阅书末的注释,收听有声书的听众也不需要参看图表。因此,本书的章节独立成篇,书中的图表也得到了详尽描述,即使不参看本书,也能理解我们的论点。我们增加注释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绝大多数注释是引文,提供了支持我们观点的数据或者佐证我们观点的文献。其二,在少数情况下,注释包含了更详尽的技术性资料,以供感兴趣的读者查阅。这些内容对于本书的正文而言并非必需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描绘绝望时经常深感痛苦,相信一些读者在读到相关内容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些正遭受我们所描述的抑郁或成瘾困扰的人可以寻求帮助。如果你有自杀的想法,请拨打美国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热线1-800-273-8255(电话)。你也可以在SpeakingOfSuicide.com/resources上找到其他协助性资源的列表。如果你本人、你的家人,或者你认识的某个人正深陷药物成瘾或酒瘾,那么我们建议你首先和一位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或精神顾问进行交谈。我们还推荐嗜酒者互诫协会,即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org)和嗜酒者家庭互助会(Al-Anon,Al-Anon.org),后者旨在帮助受影响的嗜酒者家庭成员。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为许多人提供帮助,并提供一个友善和无风险的有效支持社区。通过它们的网站,可以方便地找到其本地组织。
安妮·凯斯
安格斯·迪顿
2019年10月,写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4年夏天蒙大拿州的一间小木屋内。我们每年8月都会前往麦迪逊河瓦尔尼桥旁的小村庄度假,那里可以俯瞰麦迪逊山脉的群山。我们曾立志调查幸福感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调查在那些幸福感低下、人们声称自己生活得一团糟的县乡和城市,自杀现象是否更为普遍。纵观过去10年的自杀率,蒙大拿州麦迪逊县是我们常年居住的新泽西州默瑟县的4倍。我们对此颇为好奇,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蒙大拿州总体上过得非常愉快,并且那里的其他居民似乎也生活得很开心。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的自杀率正在迅速攀升。我们还发现另一个令我们颇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美国中年白人还遭受着其他伤痛的困扰。他们中罹患疼痛症的比例更高,整体健康状况也更差。虽然他们的总体情况略好于美国老年人——毕竟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中年人的健康状况则在恶化。我们知道,病痛会驱使人们自杀,所以或许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那只是第一步。当我们考虑如何呈现我们的结果时,我们希望把自杀现象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自杀在总体死亡情况中的比例如何?与癌症或心脏病等主要死亡原因相比,其严重程度又如何?于是,我们回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下载相关数据并进行计算。我们惊讶地发现,对美国中年白人而言,不仅自杀率正在上升,他们的整体死亡率也在攀升。虽然增加的数字不大,但考虑到死亡率应该逐年下降,因此死亡率不再下降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更不用说不降反升了。
我们以为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死亡率不断下降是20世纪最美好,也最确定的特征之一。任何一个大群体的死亡率都不应该不降反升。例外情况当然也出现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流感大暴发,或者30年前许多年轻人死于艾滋病。但是,死亡率稳步下降,特别是中年人的死亡率稳步下降,是20世纪最伟大(也最可靠)的成就之一,并且这正是推高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富裕国家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原因。
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杀事件的数量并不足以解释整体死亡趋势的逆转。我们研究了其他可能导致这种逆转的因素。令我们惊讶的是,“意外中毒”是一个重要原因。怎么会这样?难道很多人不小心误喝了通乐管道疏通剂或者除草剂?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并不知道“意外中毒”这一死因也包含药物过量使用致死,也不知道服用阿片类药物 [1] 造成的死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这种情况还在迅速蔓延。此外,酒精性肝病的死亡率也在迅速上升。因此,死亡率上升最快的三大原因包括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这些类型的死亡都属于自戕,无论是用枪迅速地自我了断,还是缓慢并且不那么确定地因为药物成瘾送命,抑或更缓慢地死于酒精中毒。我们开始将这三大死因统称为“绝望的死亡”。这主要是为了给它们贴一个标签,从而能够方便地将其联系在一起。导致死亡的究竟是怎样的绝望,到底是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心理上的绝望,我们不得而知,也未妄加臆断。但这一标签被广泛接受,而本书则是对这种绝望的一次深入探索。
本书所讲述的正是这一类死亡以及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群。我们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发现,以及我们和其他人随后的更多发现。其他作家已在新闻报道和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好书中描述过死者的名字和面容,并讲述了他们身后的故事,我们也将利用这些描述。我们自己此前的工作主要聚焦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在本书中我们更进一步,尝试追溯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哪些人正在死去?一个人死亡后,需要为其开具一份死亡证明,其中一栏需要填写死者的学历。在这一栏中,我们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增加的绝望的死亡者几乎全部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基本上未受影响,处于危险之中的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这种情况在自杀人群中尤其突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自杀率普遍较高, [2] 但在当前泛滥的绝望的死亡中,情况却并非如此。
学士学位正在日益分裂美国,它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好处成为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死亡率方面,在生活质量方面也同样如此。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饱受病痛日益增加、健康不断恶化以及严重精神压抑的折磨,工作和社交能力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这两类人群的收入、家庭稳定性和所在社区的差距也不断扩大。 [3] 学士学位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好像被迫佩戴着一枚圆形的猩红色徽章,上面写着BA(学士学位),并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像英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一样)已经逐步建立精英制度,并且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早就预言的那样,这种制度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这个概念,同时认为精英制度将导致社会灾难。 [4] 那些没能通过大学考试、成功毕业并成为大都会精英的人,在飞速发展、科技腾飞、兴旺繁荣的都市中并无一席之地,被迫接受在全球化和机器自动化生产的威胁下朝不保夕的工作。精英人群会为自身的成就扬扬自得,将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奋斗,同时鄙视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认为他们也曾被给予机会,但是却没有抓住机遇。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价值得不到认可,也不会获得尊重,他们自己往往也以失败者自居,并对社会制度不公愤愤不平。 [5] 纵观今日世界,成功可以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些未能通过精英测试的失败者就面临多大的惩罚。迈克尔·杨不无预见性地将那些被时代洪流抛弃的人群称为“民粹主义者”,将精英人群称为“伪善主义者”。
在我们的叙事中,不仅有死亡,还有病痛和成瘾,以及分崩离析和丧失意义的生活。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同居率和非婚生子女比例持续上升,结婚率则持续下降。许多中年男子并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和曾经同居的女友分手,而他们的孩子现在正和一个不是他们父亲的男人住在一起。过去那些来自宗教组织,尤其是传统教会的慰藉,现在已经从许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人们对工作的依恋度日益下降,许多人已经彻底脱离就业大军,仅有少数人拥有长期雇佣关系,雇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员工负责,而这种长期雇佣关系对许多人来说曾是地位的象征,是富有意义的生活的一个基础。
过去,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工会帮助工人提高工资,并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在许多城镇,工会议事厅是社交生活的中心。而现在,曾经支持蓝领工人的高工资已基本消失,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已被服务业工作取代,例如,医疗、食品制备和服务、保洁服务以及维护修理性工作。
我们所讲述的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和自杀的故事,关于低薪的低档工作的故事,关于婚姻解体的故事,以及关于宗教信仰下降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身上。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2018年,年龄在25~64岁的美国人口数量为1.71亿,其中62%为非西班牙裔白人,而这些人中的62%没有学士学位。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即面临上述危险的人群,占工作年龄段总人口的38%。当然,全体美国劳工阶层,不分民族和种族,均正在遭受经济力量的伤害,但黑人和白人的故事截然不同。
回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在中心城区工作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与30年后白人劳工阶层的经历颇有共同之处。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对黑人的打击尤其严重,对于这个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心城市的工作机会变得稀缺。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更有才能的黑人逐渐离开市中心地区,搬到城市中更安全的社区或者郊区。结婚率急剧下降,因为适婚男子不再拥有工作。 [6] 犯罪率迅速上升,同样上升的还有因为暴力和霹雳可卡因泛滥导致的药物过量使用和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其中艾滋病对美国黑人的冲击尤其巨大。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而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其社会地位,因为经济格局的变化造成低技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黑人群体首先受到这一负面影响的冲击。
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处境一直比白人艰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黑人的寿命都更短。黑人也更不容易上大学或者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的黑人,其平均收入水平也低于白人。黑人的财富更少,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更小,进监狱和陷入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在上述许多领域(尽管不是全部领域),黑人的处境现在都已有所改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在教育、工资、收入和财富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1970—2000年,黑人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超过白人。在21世纪前15年,黑人的死亡率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劳工阶层白人的死亡率则有所上升。
与1970年相比,公开的歧视现象有所减少。美国已经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同时,过去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同肤色的人通婚是错误的,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样做没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一些白人对丧失白人长期享有的特权感到愤恨,但这只是伤害了他们,而对黑人没有影响。 [7]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指出,主要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制度实际上损害了贫穷白人的利益。富人曾拉拢贫穷的白人,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多少钱,但至少他们是白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总结的那样,“南方贵族夺走了全部,只留给贫穷的白人吉姆·克劳法(Jim Crow) [8] ”。于是,当贫穷的白人没有钱吃饭时,“他可以吃吉姆·克劳,并自我安慰说,无论自己的日子多么糟糕,也总比黑人要好,因为至少他是一个白人”。 [9] 随着种族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日渐消失,白人劳工阶层也丧失了这些歧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超过半数的美国白人劳工阶层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已经与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同样严重,但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只有30%的人认同这个观点。 [10] 对此,历史学家卡罗尔·安德森表示,对于一个“长期享有特权的人而言,平等看上去无异于压迫”。 [11]
尽管黑人的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但过去30年间,黑人的死亡率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的死亡率的差距已明显缩小。20世纪90年代初,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多,但后来,随着前者的死亡率持续下降,后者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20%。2013年以来,阿片类药物滥用也开始蔓延到黑人社区,但在此之前,绝望的死亡只是贫穷白人的流行病。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记录了白人劳工阶层的生活如何在过去半个世纪逐步衰落。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据劳动年龄人口的62%,因此了解他们的死亡率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12] 我们对此并无多少补充,但我们仍然希望提醒大家,那个故事与今天白人的困境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西班牙裔人群则是一个涵盖多族裔的群体,划分的依据是其是否讲西班牙语。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死亡率因西班牙裔移民构成的变化(例如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或者萨尔瓦多)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意讲述一个能够囊括这一群体的统一故事。
我们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些社会和经济力量,这些力量使得劳工阶层的生活缓慢地日益恶化。其中一个论点主要关注了劳工阶层白人这一群体内部价值感的不断下降和文化的日益失调。 [13] 毫无疑问,有关非婚生子女禁忌的社会规范崩溃,最初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解放,但从长远来看,它带来了沉重的代价。那些年轻时笃信自己可以活得无拘无束,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在人到中年之后发现自己孑然一身,独自漂泊。对宗教的背弃或许与此类似,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宗教组织未能适应政治和经济变化,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继续提供意义和安慰。这些关于社会规范的论点无疑有其道理,但我们的叙事更加侧重于某些外部力量,这些力量已经逐渐吞噬半个世纪前典型劳工阶层生活所依赖的基础。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劳工阶层的灾难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对工作丧失了兴趣,但是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男性的平均工资增长已经停滞半个世纪之久。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而言,其平均收入的购买力在1979—2017年下降了13%。而在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85%。尽管2013—2017年,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收入变化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与其长期下降趋势相比,这一转机微不足道。在经济大衰退 [14] 结束后的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近1600万个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但其中只有不到300万个工作岗位针对的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针对仅有高中学历就业者的工作岗位更是只有区区5.5万个。 [15]
工资长期下降是打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一种根本性力量,但简单地将绝望与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相联系并不能解释目前发生的一切。首先,工资的下降还伴随着就业情况的恶化——从较好的工作跌落到较差的工作,许多人完全离开了就业市场,因为较差的工作没有吸引力,也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因为他们难以为了新工作搬家,也可能是以上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工作质量的下降和完全脱离就业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单纯的收入损失带来的痛苦。
其次,许多低工资工作无法带来受雇于成功企业(即使只是一名低级雇员)的自豪感。当清洁工、看门人、司机和客服代表直接受雇于一家大公司时,他们归属于这家公司,但是当这家大公司把这些工作外包给只能支付很低的薪水且没有晋升机会的商业服务公司时,这些雇员则不再归属于该公司。即使工人们从事与外包前相同的工作,他们也不再是这家大公司的一部分。正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发人深省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人不再被邀请参加公司的假日聚会。 [16] 如今,柯达公司的看门人一路晋升,最终成为集团旗下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7] 而且在上面提到的工作中,一些工作现在受到软件的密切监控,这些软件完全剥夺了工人的控制权或主动权,堪比旧时代那些被工人深恶痛绝的装配线。 [18] 与此相反的是,即使是矿工等从事危险和肮脏工作的工人,或是知名大公司的低级职员,也能够因为自己的职业角色感到自豪。
没有前途的男人不可能成为好的婚姻伴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的结婚率开始下降,更多的人失去了婚姻带来的好处,包括不再有机会见证孩子的成长以及失去含饴弄孙之乐。目前,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母亲平均至少有一个非婚生孩子。暗淡的前景使人们更难建立像他们父母一般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家庭或者攒钱送孩子上大学。高薪工作的匮乏威胁着社区及其可以提供的服务,如学校、公园和图书馆。
工作不仅是金钱的来源,也是劳工阶层生活中的仪式感、习俗和惯例的基础。当工作遭到破坏,传统劳工阶层的生活最终将不复存在。伴随着婚姻和社区的消失,意义、尊严、骄傲和自尊也丧失殆尽,随之而来的将是绝望。劳工阶层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甚至可以说,金钱并非他们的主要损失。
我们的论述呼应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杜克海姆对自杀的论述,即一旦社会无法为某些成员提供框架,使他们能够在此框架中过上有尊严和有意义的生活,自杀现象就会出现。 [19]
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困境,尽管经济困境无疑存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并不是美国最贫穷的群体,他们几乎不太可能比非洲裔美国人更穷。因此,我们认为,工资下降实际上正在逐渐摧毁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现行经济体制辜负了劳工阶层?如果我们希望提出变革建议,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应从哪里开始变革,以及什么政策可能发挥作用。
无疑,我们依然可以转而批评人们应该对自身的失败负责,并宣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不可能成功,因此这些人要做的只是接受更多的教育。我们并不反对教育,并且认同教育的价值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升。我们也期望建立一个新世界,能让每个人都从接受大学教育中受益,而且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意愿,并有能力这样做。但我们无法认同如下基本前提,即除非人们拥有学士学位,否则他们就对经济毫无贡献。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那些得不到学士学位的人不应得到尊重,或者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人们往往将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视为造成当前局面的元凶,因为它们降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价值,并以更便宜的外国劳动力或更便宜的机器取而代之。然而,其他富裕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同样面临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但没有出现工资增长的长期停滞,也没有发生绝望的死亡的大流行。因此,美国一定发生了某些对劳工阶层特别有害的事情,本书的主体部分就试图找出这些因素。
我们认为,医疗制度已成为美国特有的灾难,正在破坏美国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想指出,美国的市场和政治力量已经逐渐远离劳动人民转而为资本服务,其程度远甚于其他国家。全球化对这种转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既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又赋予了雇主更大的权力, [20] 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则将其推到比其他国家更为极端的地步。随着工会的衰落,以及政治环境对公司越来越有利,公司日益变得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于苹果和谷歌等高科技公司的惊人发展。相对于其规模,这些公司的员工数量非常少,单个员工创造的利润则相当高。这对生产力和国民收入而言都是好事,但工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则几乎无法分享任何收益。更不乐观的是,美国一些行业的整合——医院和航空公司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已经使得某些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势力 [21] 大大增强,这使得企业有可能将价格提高到自由竞争市场应有的水平之上。一方面,公司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工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不断下降,这使得公司能够以牺牲普通人、消费者,特别是工人为代价获取利益。最糟糕的是,得益于这种权力,一些受政府许可保护的医药公司已经从销售被虚假宣传为安全的成瘾性阿片类药物中赚取数十亿美元,以戕害生命为代价赚取利润。总而言之,美国的医疗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一种制度如何在政治的保护下,将收入向上分配给医院、医生、设备制造商和制药厂,却同时为国民提供富裕国家中最糟糕的健康保障。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2019年8月,阿片类药物制造商正在面临司法诉讼,一名法官下令强生公司向俄克拉何马州支付超过5亿美元的赔偿。强生的一家子公司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种植罂粟,这些罂粟是美国生产的几乎全部类阿片药物的原料。早前还曾有报道称,奥施康定 [22] 的生产商普渡制药这家最臭名昭著的制药公司将达成一项协议,意味着拥有这家公司的萨克勒家族可能会失去公司控制权,并吐出其在过去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然而,针对医生和病人的积极药物营销仍在进行,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仍然批准使用此类实际上属于合法海洛因的药物。许多一直密切关注阿片类药物丑闻的人都认为,这些合法毒品贩子的行为与遭到普遍鄙视和谴责的非法海洛因或可卡因毒贩并没有什么区别。 [23]
医疗行业的问题远不止阿片类药物丑闻这一项。美国花费了巨资,却造就了西方世界最糟糕的国民健康状况。我们想说,这个行业已经成为生长在经济制度心脏部位的癌症,并已全面扩散。它使工资降低,毁掉了好的工作,并且让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越来越难以满足其选民的基本需求。公共利益和普通人的福祉让位于那些本已富得流油的人的私利。如果没有那些本该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客的默许乃至时不时热情参与,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说罗宾汉抢劫富人是为了造福穷人,那么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一切则恰恰与罗宾汉所做的相反,是劫贫济富,或许这可以被称为诺丁汉郡治安官式再分配 [24] 。政治保护正被用于个人致富,帮助富人掠夺穷人,这一过程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称为寻租。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并且同时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反对,前者是因为其不公的分配结果,后者则是因为它破坏了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市场。寻租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斯密在其《国富论》这本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圣经”的巨著中指出,尽管税法可能非常严苛,但与“我们的商人和制造商为支持其荒谬与压迫性的垄断而胁迫立法机关制定的”某些法律相比,税法可谓是“温和有加的”。他指出“这些法律可以说完全是以鲜血写就的”。 [25] 寻租是导致美国劳工阶层工资增长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与绝望的死亡存在很大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不吐不快之言。
谈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工厂关闭并迁移到墨西哥或中国,同时生产自动化使机器取代了工人。这些因素的确真实存在,并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础。但是,正如其他富裕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所有国家都面临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冲击,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美国那样使工资下降,更不用说导致大量的死亡。事实上,美国的医疗制度对此应承担很大的责任,同样应受责备的还有政策,特别是在通过反垄断政策约束市场势力方面的失职,这一点在劳动力市场甚至比在商品市场更甚。此外,还要加上政策未能有效地控制制药公司、医疗公司、银行和许多中小企业主(例如医生、对冲基金经理、体育特许经营权所有者、房地产商人和汽车经销商等)的寻租行为。上述所有人都通过“压迫性的垄断”与特别交易,税收减免,以及“胁迫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致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的人口以及这些人中的前10%,大多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自己经营企业的企业家, [26]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寻租行为中获益良多。
不平等现象极其有害,它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平等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如果富人能够通过不公平的程序压低工资和提高产品价格,并从中渔利,那么肯定会加剧不平等。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致富。有些人发明了新的工具、新的药物、新的设备,或者新的做事方式,从而造福了众生,而不仅仅是使他们自己获利。他们通过改善和延长他人的生命而获得收益。伟大的创新者致富是一件好事。创造与索取并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导致不公平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过程。
落在后面的人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区的丧失,他们并不关心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或者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到底有多少财富。但是,当他们认为不平等来自作弊或特殊待遇时,他们将无法忍受。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问题。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银行家做事可靠,他们获得高薪理所应当,因为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损失惨重,包括失去他们的工作和住房,而银行家们却继续拿着高薪,并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于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劫贫济富的骗局,而非推动整体繁荣的引擎。
我们并不认为征税是解决寻租问题的好办法。阻止小偷的正确方法是不让他们偷窃,而不是给他们加税。 [27] 我们需要阻止阿片类药物被滥用,而不是对贩卖药物得来的利润征税。我们需要修正过程,而不是试图修正结果。我们需要让外国医生更容易获得在美国执业的资格。我们需要阻止银行家和房地产商出于自身利益制定法规和税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工资停止增长,甚至不断下降,而并非不平等本身。事实上,许多不平等恰恰是由于人为压低工资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造成的。减少寻租行为将大大减少不平等现象。当一家制药公司的老板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游说集团说服政府批准高价格,延长其专利和许可期限,以及其他便利他们的法规而获得惊人的财富时,他们极大地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一方面,他们压低了那些必须为药品买单的患者的真实收入;另一方面,他们还推高了处于财富分配顶端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修改破产法,以通过牺牲借款人利益而使其自身得益的银行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组织有序、资金充足的运动来改变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力平衡”。 [28]
正如人们经常注意到的那样,即使对富人征收所谓的“没收税”也并不能给穷人带来多少救济,因为穷人太多,富人太少。然而,在当今世界,我们需要思考反方向过程的影响,即从大量劳动人口的每一个人身上榨取哪怕一点点钱,也能为正在攫取财富的富人提供巨大的财富。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阻止它。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不仅仅为了精英阶层,也能够惠及普通大众?我们很容易感到悲观。一旦政治权力和金融权力不断集中,这种态势将不会自我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十分正常,但这只是人们沮丧和愤怒的一种表达,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白人劳工阶层不相信民主能帮助他们。2016年,超过2/3的美国白人劳工阶层认为选举已经被富人和大公司掌控,因此他们是否投票并不重要。政治学家对美国国会投票模式的分析佐证了他们的这种怀疑。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立法者,总是投票支持他们更富裕选民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利益置之不理。 [29]
19世纪末,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曾发起反对巨型托拉斯不当行为的运动,他后来被伍德罗·威尔逊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并成为美国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他认为极度不平等不符合民主原则。这既适用于“好”的不平等,也适用于“坏”的不平等。如果那些合法赚取财富的人利用它损害穷人的利益,那么人们获取财富的方式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制约极端不平等背后的寻租、游说和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以终止获取财富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高边际所得税,或更有效(但更难实施)的财富税也可以减少财富对政治的影响。但我们有时候很难感到乐观。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不平等状态一旦确立,就只能通过暴力的决裂来打破,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已经证实这种观点。 [30]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太过悲观,但是,除非能够对导致不平等的过程和制度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很难改善当前的不平等状况。
当然,还是有一些值得乐观的理由,即使在我们目前这样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下,依然有一些政策是可行的,并可能会使情况有所改善。制度可以改变。围绕这些问题有很多思想上的争论,还有许多很好的新想法,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加以讨论。但现在,我们希望以一个更乐观的史实结束引言。
19世纪初,英国的不平等现象远远超过美国今天面临的情况。世袭的土地所有者不仅极其富有,而且通过严格控制选举权控制议会。1815年后,由于臭名昭著的《谷物法》禁止进口小麦,英国国内粮食价格暴涨,几乎出现饿死人的局面。虽然小麦的高价极大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但却非常符合地主贵族的利益,因为后者依靠对进口的限制而坐享租金收益(这是一种经典和符合字面意义的寻租)。这种寻租行为并没有因为饿殍遍地而停止,“以鲜血写就”的法律不断推出。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创新和发明大量出现,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然而劳动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随着人们从相对健康的农村移居到臭气熏天、卫生状况极差的城市,死亡率不断上升。每一代新兵的身高都比上一代更矮,说明平民在童年时营养不良的状况日趋严重,这既是由于他们吃不饱,也是由于卫生条件恶劣。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不断丧失,其原因可能仅仅是教堂都在农村地区,新兴工业城市并无教堂。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并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利润在上升,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很难预测这一过程能够产生积极结果。
到19世纪末,《谷物法》已经不见踪影,贵族的租金和财富也随着全球小麦价格下跌而减少,特别是1870年美国大草原的小麦进入市场之后。一系列的改革法案不断扩大选举权,从19世纪初仅有10%的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扩大到世纪末50%以上的男性拥有选举权,尽管妇女等到1918年才获得了选举权。 [31] 到1850年,工资开始上涨,死亡率也已开始下降,并持续了长达一个多世纪。 [32] 这一切并没有导致英国崩溃,也没有出现战争或流行性传染病,渐进式的改革体制逐步照顾到那些被抛弃的人的需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这一逻辑是否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时代,但事实本身至少可以证明,我们有理由保持有限的乐观。
[1] 阿片类药物有镇痛和中枢神经系统镇静作用,主要用于中到重度疼痛的治疗,比如癌症的疼痛,但容易成瘾,常见的包括海洛因、吗啡、芬太尼、杜冷丁、美沙酮等。——编者注
[2] Emile Durkheim, 1897, 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 , Germer Baillière, but the link with education goes back further. See Matt Wray, Cynthia Colen, and Bernice Pescosolido, 2011,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37, 505–28.
[3] Sara McLanahan, 2004, “Diverging destinies: How children are faring unde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y , 41(4), 607–27; Andrew Cherlin, 2014,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 ca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Robert D. Putnam, 2015,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 Simon and Schuster; David Goodhart, 2017,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 Hurst; Charles Murray, 2012,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 ca, 1960–2010 , Crown.
[4] Michael Young, 1958,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 Thames and Hudson.
[5] Michael Sandel, 2018, “Popu 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open Democracy, May 9, https:// www.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democracy/.
[6]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
[7] Carol Anderson, quoted in Susan B. Glasser and Glenn Thrush, 2016, “What’s going on with America’s white people?,” Politico Magazine , September/October 2016.
[8] 吉姆·克劳是美国戏剧演员托马斯·赖斯扮演得一个黑人角色,后来逐渐演变为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编者注
[9]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65, “Addres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 March 25, Martin Luther King, J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Stanford, https:// kinginstitute.stanford.edu/king-papers/documents/address-conclusionselma-montgomery -march.
[10] Daniel Cox, Rachel Lienesch, and Robert P. Jones, 2017, “Beyond economics:Fears of cultural displacement pushe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to Trump,” PRRI/Atlantic Report, April 9, https://www.prri.org/research/white-working-class-attitudes-economytrade-immigration -election-donald-trump/.
[11] Anderson, quoted in Glasser and Thrush, “What’s going on.”
[12] Wilson, Truly disadvantaged ; Charles Murray,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 Basic Books.
[13] Murray, Coming apart .
[14] 经济大衰退指由2007年8月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危机又被称作金融海啸,是由美国次级房贷信贷危机引发的流动性危机。2008年9月。危机开始蔓延至其他经济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这是自大萧条(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通常它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二严重的经济衰退。——译者注
[1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5, “Table A-4: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25 years and over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 Retrieval: Labor Force Statistics (CPS), July8, https:// www.bls.gov/webapps/legacy/cpsatab4.htm.
[16] Nicholas Bloom, 2017, “Corporations in the age of inequality,” The Big Idea,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cover-story/2017/03/corporations-in-the-age-ofinequality.
[17] Neil Irwin, 2017, “To understand rising in equality, consider the janitors at two top companies, then and now,”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2, https:// www.nytimes.com/2017/09/03 /upshot/to-understand-rising-inequality-consider-the-janitors-at-two-topcompanies-then -and-now.html.
[18] Emily Guendelsberger, 2019, On the clock: What low- 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 , Little, Brown; James Bloodworth, 2018, 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 wage Britain , Atlantic Books.
[19] Durkheim, Le suicide .
[20] Dani Rodrik,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1] 市场势力(market power)也叫市场权力,是指卖方或买方不正当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通常代表卖方或买方具有垄断倾向。——译者注
[22] 奥施康定(OxyContin)是普渡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处方类阿片类止痛药,曾是美国广受欢迎的止痛神药,后被曝存在致瘾风险。——译者注
[23] Sam Quinones, 2015, Dreamland: The true tale of Ameri ca’s opiate epidemic ,Bloomsbury.
[24] 侠盗罗宾汉的故事发生在英国诺丁汉郡,邪恶的诺丁汉郡治安官是与罗宾汉对抗的反面人物。——译者注
[25]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 bk. 4.
[26]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2019, “Capi tal 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4), 1675–745.
[27] 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2016,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8] Charles Jordan Tabb, 2007, “The top twen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onsumer bankrupt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 1, 9–30, 29.
[29]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2011, Winner- take- 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 Simon and Schuster; Martin Gilens, 2012,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 cal power in Ameri 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rry M. Bartels,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 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0] Walter Scheidel, 2017,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1] David Cannadine, Victorious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1800–1906 ,Penguin.
[32] Robert C. Allen, 2017,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自1990年以来,美国平均人口寿命每6年就会增加一岁。现在出生的孩子的可预期平均寿命为78岁左右,比1900年出生的婴儿增长了近30岁。从我出生直到今天,心脏病的致死人数已减少超过70%。随着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的进展,自该病毒在30多年前出现以来,我们现在首次有望看到摆脱艾滋病威胁的一代。过去15年,癌症死亡率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下降。
——弗朗西斯·柯林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HIS)院长
参议院证词,2014年4月28日
进入20世纪,美国国民健康状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到2000年,人类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已成为大家期待的常态。儿童的寿命长于他们的父母,而他们父母的寿命则比自己的父母更长。一代又一代人的死亡危险度不断降低。更好的健康状况得益于更好的生活水平,药物和治疗方法的进步,也得益于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行为(尤其是吸烟)对健康的影响,因此改变了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其他富裕国家因为同样的原因实现了类似的进步。贫困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则更为惊人,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2000年,所有这些进步似乎都将继续下去,成为大势所趋的事实。
同期的经济进步也非常显著。2000年,与出生于1901年(这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出生)的祖父母、曾祖父母或曾曾祖父母相比,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加富裕,而这些先人的生活已经比生活在此前一个世纪(1800—1900年)的先祖更为优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间,即在法国被称为“黄金30年”的时期,西欧和北美富裕国家的收入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那些年里,美国不仅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而且无论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级,都普遍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果实。
教育领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1900年,只有1/4的人能够读到高中毕业。到20世纪中叶,已经有3/4的人口高中毕业,而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也从5%上升到20%。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收入通常比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高,但战后中期的就业市场为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无论是钢铁厂还是在汽车厂的工作,都可以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尤其是人们可以沿着社会阶梯不断爬升,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男性跟随父亲的脚步,获得工会支持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对于工人和公司双方而言都有终身承诺。工人的工资足够高,可以支持一个男人结婚、成家、买房,在许多方面都享受比父母在同年龄段更好的生活。为人父母者会考虑送孩子上大学,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那是所谓的蓝领贵族时代。
当然,我们绝对无意辩称20世纪是人类的天堂乐园,而我们在21世纪失去了它。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的了。
20世纪发生了许多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并导致数千万乃至数亿人丧生。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等的残暴政权导致了令人发指的大量人口死亡。除此之外,还有致命的流行病,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流感和20世纪末的艾滋病。甚至在人们已经了解如何预防一些儿童常见疾病之后很久,全球仍有数百万儿童死于这些疾病。战争、大规模杀戮、流行病和不必要的儿童死亡导致预期寿命下降,有时是极大的下降。人类还经历了诸多经济灾难,福祉远未得到普遍分享。大萧条给数百万人带来了贫困和苦难。“吉姆·克劳法”多年盛行,以制度化的方式剥夺美国黑人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权利。
我们并不想宣称人类一直享有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只是想强调,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例如,1900—2000年,人类死亡的风险不断降低,繁荣的可能性则不断增强。人类在某些方面取得的进步更大,同时某些国家的发展好于其他国家。但是,由于20世纪很长时期内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不断进步,到20世纪末,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期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他们的孩子也能像他们自己一样,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末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长寿。不仅如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保持如此稳定和持久的进步,我们的后代会生活得更好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一件事。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历史进步,以及我们将在本书中描述的不那么积极的变化,我们需要澄清进步是如何被衡量的。
我们经常谈到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是对立的关系。死亡率衡量死亡的情况,而预期寿命衡量寿命的长短。死亡率是指死亡的风险有多大,预期寿命是指新生儿能活多少年。在死亡率高的时期或者地区,预期寿命会比较低,反之亦然。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并不相同——婴幼儿的死亡率高,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死亡率较低。人到中年时,死亡的威胁再度开始显现,人到了30岁后,死亡的风险逐年增加。2017年,美国30~31岁人口的死亡率为1.3‰,到40岁时死亡率增至2.0‰,到50岁时达到4.1‰,到60岁时则达到9.2‰。对中年人而言,每过10年,死亡的概率就会加倍。在其他富裕国家,死亡的风险会略低一点,但在没有流行病或战争的情况下,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地区和所有时期。
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生活可以被看作一场跨栏赛跑,每个生日都需要跨越一个栏架。死亡率是指在跨越每个栏架时跌倒的概率。这个概率在开始时很高,直到这个新生儿可以迈开大步向前冲,然后在一段时间内,死亡率将变低,因为随着经验的增加,跑步的人能够更容易地应付每一个栏架,再然后,随着跑步者开始疲劳,死亡率在中年和老年时期会越来越高。在本书中,我们将讨论预期寿命(一个普通的新生儿可以跨越多少个栏架)和死亡率(其在跨越每个栏架时跌倒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将要描述的事件对不同栏架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而它可能会导致中年人的死亡风险增高,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却降低。如果这些影响恰好相互抵消,则它们就根本不会在预期寿命变化上得到反映。
如果在一开始时栏架很高,那么没有多少人能跑得太远。在20世纪初,美国儿童面临很高的死亡风险。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充足或者足够好的食物,麻疹这样的儿童疾病往往会导致儿童送命,疫苗接种远未普及,美国许多地方尚未能保证饮用水的安全,例如,未能将污水处理与饮用水供应进行适当分隔。如果住在上游的人将河流当作厕所,而下游居民则以河水为饮用水,那么不仅令人恶心,而且极其危险。提供安全的水源和良好的卫生条件的成本相当高,即便基本的科学常识,例如细菌致病理论已经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美国公共卫生官员也花了很长时间在全国推行这些措施。
除了刚出生那几年之外,死亡的概率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加。婴儿和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最高。富裕国家中的婴儿相对是安全的,每1000个美国婴儿中,只有6个无法活到一岁生日。其他国家的情况甚至更好,例如,瑞典和新加坡的婴儿死亡率仅为2‰。
一些贫困国家的风险则要高得多,但那些国家也迅速取得了进步。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高于50年前的水平。
在20世纪,美国新出生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从49岁增加到77岁。到20世纪末,即1970—2000年,预期寿命从70.8岁增加到76.8岁,即每10年增加两岁。从1933年,即美国开始全面统计数据时起,这种积极的趋势几乎一直得以保持,即使预期寿命暂时出现下降,也不会超过一两岁。虽然1933年之前的数据并不完整,因为当时并非所有州都有记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流感暴发期间,即1915—1918年,预期寿命似乎出现了下降。
如果这一增长趋势得以持续,到2100年,预期寿命将超过90岁,相当一部分人将活到100岁。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1900年,人类的三大死亡原因均是传染性疾病,即肺炎、肺结核和胃肠道感染。到20世纪中叶,随着公共卫生项目和疫苗接种计划基本完善,加上抗生素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传染病已逐渐不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命之初需要跨越的栏架降低,于是死亡主要发生在中老年时期。死亡本身也逐渐变老,从儿童的肠道进入中老年人的肺部和动脉。进入这个时期后,预期寿命将很难提高。减少生命之初需要跨越的栏架,将极大地影响人们能跑多远,但是,一旦几乎每个人都能步入中老年,那么挽救老年人的生命很难大幅提高预期寿命。
到20世纪末,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已经成为心脏病和癌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戒烟,心脏病和肺癌的发病率也随之下降,吸烟人数大幅减少对死亡率下降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样对此有极大贡献的还有心脏病的预防性治疗。
降压药的价格十分便宜,且服用方便,有助于控制血压,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胆固醇,从而有助于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发作。心脏病死亡率的降低是20世纪最后25年的重大成就之一。此外,人类也已经成功研制出针对某些癌症(包括乳腺癌)的新药和筛查方法。
新药对于降低死亡率的贡献可能不如人类自身行为的改变,但它们显然能够拯救生命。当我们在本书后面探讨医药行业的过度行为时,你也应该一直记住,药物的确拯救了许多生命。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没有阿司匹林或布洛芬,没有麻醉剂,没有降压药,没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者没有避孕药,我们的世界无疑将是一个更糟糕的所在。公共政策的关键难题是找到一种途径,使人们既能够享受更长久和更好的生活,又不会造成社会无法接受的后果,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无法承担的财务成本。
随着某些疾病被消灭、某些疾病被控制,它们也逐渐让位,不再是致死的主要原因。而新的主要致死原因大多并非突然凭空出现,而是已经存在很久,只不过与原来那些大规模致死因素相比,它们的杀伤力相形见绌。某些死亡原因,例如老年痴呆症或晚期癌症,原来之所以并不突出,仅仅是因为当时人们很少能活到这些病症出现的年龄。其他原因,例如意外事故、自杀或糖尿病,过去就已存在,但是在天花或霍乱暴发的时代,它们并非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甚至在更近的时期,它们与肺结核或儿童痢疾相比,也只能算是次要的杀手。随着人类渐渐远离流行性传染病,致病原因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感染都是通过某种媒介,如细菌或病毒传播的,因此,发现人体或传播途径中的生物机制,如脏水、蚊子、跳蚤或老鼠,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病因,还可以提供治愈甚至消除这种流行性疾病的潜在途径。
但是生物学从来不是万能的,人们在哪里生活以及如何生活始终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对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来说,或者自杀、中毒、意外事故,生物学通常不如人们的行为或其所在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重要。
正如伟大的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指出的那样,1848年斑疹伤寒流行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和政治参与的缺失。微生物学的奠基者罗伯特·科赫找到了导致霍乱、结核病和炭疽病的细菌。他曾骄傲地写道:“人们直到现在都习惯于把结核病视为社会苦难的结果,并希望通过减轻生活的痛苦来减少疾病。但是在与这场可怕的人类瘟疫进行的最终战役中,人们将不再需要对抗一种不确定的东西,而是与一种实实在在的寄生物做斗争。” [1] 生物学与人类行为到底谁更重要,这是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老问题。在我们将要讨论的死亡事例中,行为通常是关键因素,因而我们将不会太关注那些实实在在的细菌。我们不需要太多生物学知识就能够理解枪支如何杀人,或者交通事故如何致残,然而生物学可以使我们知道,饮食控制和运动将如何影响肥胖的产生,压力如何导致疼痛,酒精如何破坏肝脏,或者吸烟如何导致心脏病。在分析问题时,我们需要时刻牢记兼顾社会科学和医学。
图1-1阐明了上述想法。这张图显示了1900—2000年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情况,曲线显示的是45~54岁白人男性和女性每年的死亡率。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其他年龄段的死亡率,但我们将经常强调这个中年年龄段。由于中年阶段正是死亡率开始上升的时期,因此它往往是观察死亡率变化趋势的绝佳年龄段。中年早逝的人口数量并不算多,通常以每年每10万人口中的死亡人数来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在1900年,每年每10万中年人口中死亡人数为1500(每年1.5%),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400(每年0.4%)左右,降幅超过2/3,这是该图最显著的特点。在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其他年龄组以及不同族裔和种族群体的死亡率也同样出现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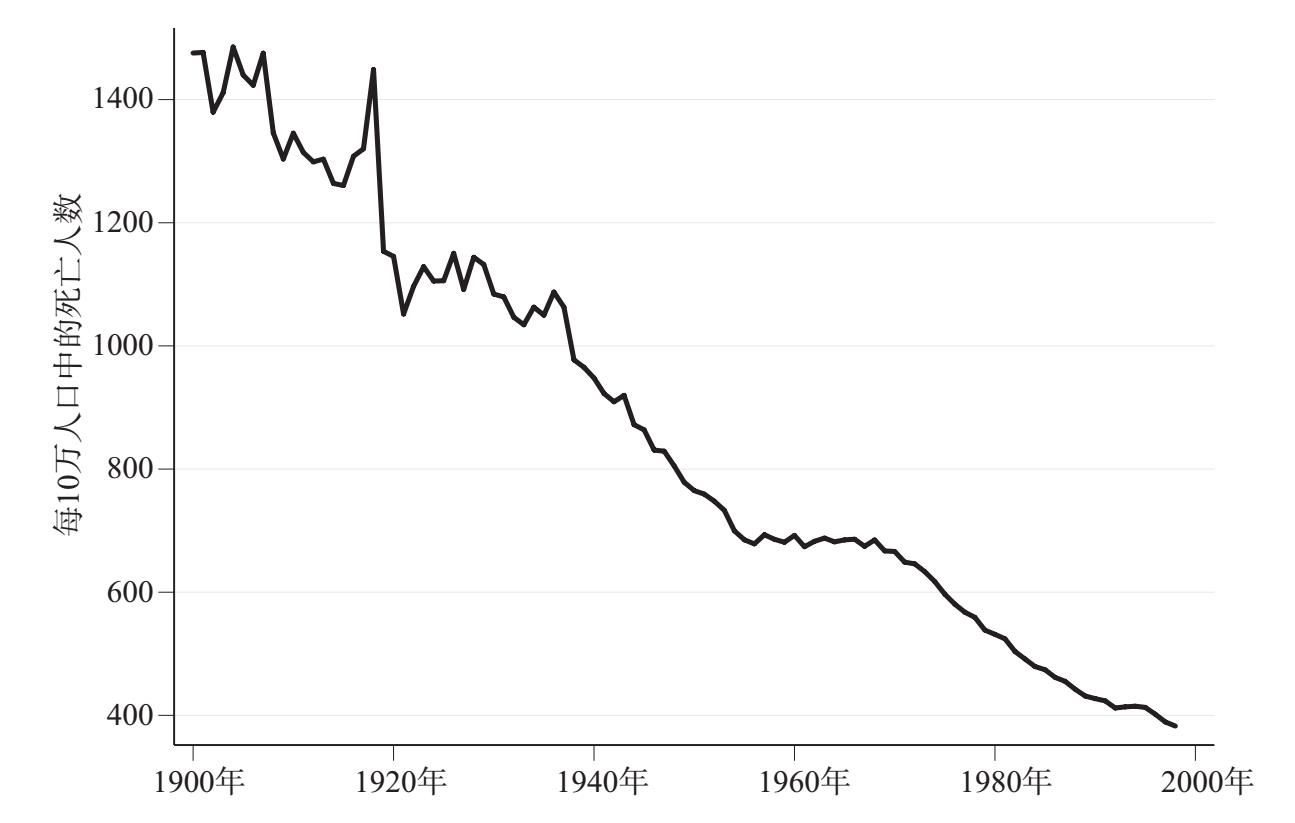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本图还反映了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件。例如,1918年死亡率激增,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席卷美国和世界的流感疫情。20世纪30年代和大萧条期间,死亡率下降的步伐有所放缓,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下降速度同样缓慢,从而表明死亡率与经济状况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的记录后,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即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死亡人数往往更高。 [2] 1960年前后,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停滞好几年,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在二三十岁时大量吸烟的人在那些年集中因肺癌和心脏病而去世。1970年之后,得益于心脏病致死率的下降,中年人口死亡率恢复了稳步下降的趋势。随着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得到普及,以及医生大量开出控制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药物,1970年之后,美国中年人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其他富裕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图1-1反映了导致死亡的所有主要因素。流行性疾病因素以流感为代表,同时其自身又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社会和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影响。人类行为因素主要表现在吸烟的影响,医学知识因素表现在人们对吸烟危害的了解,而医疗制度因素则表现在对高血压的控制之上。
图1-1只研究了45~54岁的白人。事实上,其他群体也受益于20世纪死亡率下降的趋势。非洲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的死亡率高,预期寿命也更短。这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今天仍然如此。但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同样也已逐步降低,并且下降幅度高于白人,从而使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老年人的死亡率也有所下降。1900年,一位60岁的美国女性预计可以再活15年,同样年龄的男性预计可以再活14年。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女性预计可以再活23年,男性再活20年。
相对于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发病率(导致生病而非死亡)的趋势并不十分了解。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人们不仅比过去活得更长,生活也更美好和更健康。对于过去25年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调查中获得直接的衡量标准。这些调查询问人们关于残疾、疼痛以及他们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曾经有人担心,随着人们越活越久,他们在老年时将饱受痛苦和残疾的折磨,虽然人没有死亡,但是活得并不健康,所幸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医学的进步不仅降低了死亡率,还帮助人们活得更好。关节置换术可以帮助关节丧失了功能的病人减轻疼痛,并让人们正常生活,没有它人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白内障手术能让那些本来将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药物在很多时候能够有效地减轻疼痛,缓解抑郁和其他精神困扰。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变得更加高大,这体现了他们童年时期营养和公共健康条件的改善。1980年出生的美国男性在成年后将比一个世纪前出生的男性高约3.8厘米,其他富裕国家的情况甚至更好。美国人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但是现在他们的身高已经被德国人、挪威人,尤其荷兰人超越,这也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并非万事大吉。 [3]
[1] Quoted in Paul Farmer, 1999,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e modern plag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
[2] William F. Ogburn and Dorothy S. Thomas, 1922, “The influence of the business cycle on certain social condi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8(139), 324–40; Chris-topher J. Ruhm, 2000, “Are recessions good for your heal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5(2), 617–50.
[3] John Komlos and Benjamin E. Lauderdale, 2007, “Underperfor mance in affluence: The remarkable relative decline in U.S. heigh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 88, 283–305,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37.2007.00458.x.
时至20世纪末,贯穿整个世纪的乐观主义情绪几乎消失殆尽。美国中心地带的城镇,那些曾经的钢铁、玻璃、家具或鞋子之都,以及七旬老者深情怀念的成长胜地,现在已经被摧毁。那里的工厂已经关闭,商店橱窗也已用厚厚的木板封住。在一片狼藉之中,酒精和毒品的诱惑导致许多人迈向死亡。这些故事大多从未被人讲述。每当死亡涉及自杀、药物过量使用或酒精中毒时,羞耻通常会使人们在讣告中抹去逝者的死因。成瘾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缺点,而不是一种疾病,人们相信成瘾导致的恶果最好被隐藏。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比如某位著名的厨师自杀,或者某位音乐才子死于过量服用芬太尼,抑或震动整个社区的某个死亡事件,例如女议员安·麦克莱恩·库斯特报告的一例:“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基恩的小镇,地球上再没有一个比这里更静谧的地方了,一位受人爱戴的高中教师和三个孩子的母亲,死于海洛因摄入过量。” [1] 每个故事都是真实而令人悲伤的,但我们需要站在更高处审视它们。如果审视死亡的总体数字,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巨大、更加可怕,也更加悲惨的故事。媒体报道的事件都是根据其新闻价值而选择出来的,名人会受到关注,而成瘾或自杀未遂的大新闻往往来自那些已经习惯生活在媒体聚光灯下的人。抓人眼球和不寻常的死亡,例如,名人自杀或因药致死的事件被详尽报道。普通人的死亡则很少登上头条,尽管他们同样也留下了心力交瘁的家人和朋友。新鲜出炉的事件是新闻,长期趋势则是昨日旧闻(通常意味着根本不是新闻)。死于肺癌、心脏病或糖尿病本身并不是新闻——肺癌不像埃博拉或艾滋病,尽管它夺走了更多的生命——我们只是会在阅读讣告时偶然碰到它们。如果不用数字做比较,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我们是在关注一个事件还是在处理更大的问题。所谓事件,是指如飞机失事或恐怖袭击,尽管它们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但它们令人极为震惊并具有新闻价值,又或者某种疫情的流行,比如埃博拉或“非典”,它们让许多人胆战心惊,其实真正因此死亡的人很少。更大的问题则是指那些事实上威胁公众健康,并终结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类健康进步的事物。
美国所有的死亡病例都会被呈报给当局,这些信息被汇总至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某个人死亡后,在其死亡证明上可搜集到大量信息,过去30年,这些信息中还包括死者达到的最高受教育水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有一个数据库,使用了一个颇为吸引人的名字——CDC Wonder(CDC想知道),那里能够查到很多信息,甚至可以下载和查阅删去保密信息(如姓名和社会保险号码)后的死亡证明。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和故事一样让人难过。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1900年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为每10万人有1500例,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每10万人有400例。现在,让我们跟随中年人口迈入21世纪。
我们还可以观察其他一些像美国一样人均收入较高,并且分享和应用了相同的科技与医学知识的国家。1945年后,这些国家中年人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且与美国一样,下降的趋势在1970年后不断加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在几乎所有富裕国家,45~54岁的死亡率平均以每年2%的速度稳步下降。
图2-1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分道扬镳”的画面。法国、英国和瑞典的中年人群死亡率持续下降,其他未在图中显示的富裕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进步。然而,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则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画面。这一白人人群的死亡率没有与其他国家步调一致地继续下降,而是完全停止下降,甚至掉头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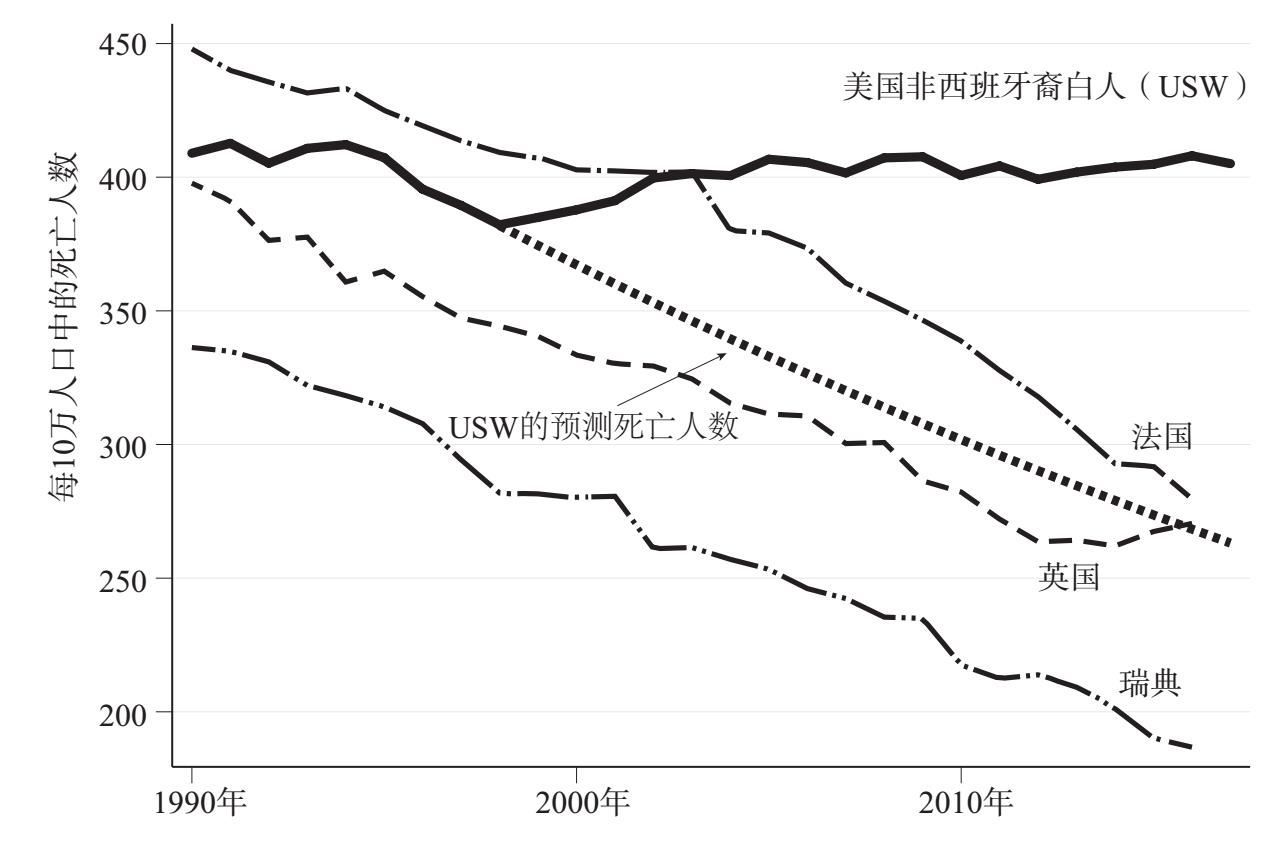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人类死亡率数据库
图中那条粗的虚线则显示了我们根据20世纪的情况所预测的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趋势。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明显偏离了其他富裕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偏离了我们曾经预测的方向。
显然,一些重要、可怕并且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有中年白人男性和女性受到了影响,还是其他年龄组也受到了影响?男性受到的影响大于女性,还是女性受到的影响大于男性?其他人群的情况又如何?这种现象是集中在特定地区,还是美国各地都是如此?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后面我们将看到,酒精、自杀和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流行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讨论它们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其他一些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在描述20世纪中年人死亡率下降的趋势时已经注意到,其他年龄组也显示了同样的积极趋势。但图2-1中的反转并非普遍存在。在后面我们将看到,较年轻的年龄组的死亡率趋势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但老年人的死亡率则延续了20世纪末的趋势继续下降。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将看到,这种逆转已经开始影响老年人口中最年轻的那一部分人口。
在图2-1中,我们的数据反映的不是所有白人而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情况,这是一个较小的人群类别,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这一人群的数据并不存在。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大大低于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但他们的死亡率却低于后者,而且其死亡率变化与其他国家同步,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图中显示的阶段,他们的死亡率与英国人口同期的死亡率相似。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高于图中所示的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但其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也比图中所示的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都快。1990—2015年,美国中年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的差距急剧缩小,但随后,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也停止下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可能也与阿片类药物有关。不同种族死亡率的差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如果认真回顾历史,我们将发现,黑人与白人死亡率的差异可以说得通。这种差异与其说与种族有关,不如说与人们所在的时期有关。我们将在后面对此加以论证。
我们现在还远未完全明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种族和族裔死亡率的差异,但其确实已经存在许多年。人们普遍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在死亡率方面的糟糕表现与他们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的表现一样,与他们长期遭受歧视和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机会较少有关。 [3] 针对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寿命长于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现象,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其他群体,例如亚裔美国人在死亡率方面的表现甚至优于西班牙裔或白人美国人。有关近年来三大主要人群在死亡率方面迥异的走势,我们将在整本书中反复探讨,尽管我们希望在一开始即坦率承认,我们将发现许多难以解释之处。
图2-1中的数据包含男性和女性,因而确实有潜在的误导性。由于各年龄段女性的死亡率均比男性低,因此女性的寿命更长。在美国,女性寿命大约比男性长5年。男性和女性会患上不同的疾病,并且相同疾病和行为对男性与女性造成的影响也不相同,例如,男性自杀的概率是女性的三四倍。但是,死亡率变化的逆转,即从20世纪的持续下降,到21世纪的停滞乃至掉头向上,在中年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尽管女性的逆转幅度比男性要大一些。即便考虑上述因素,由于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与其他国家以及原本预期的死亡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将男性和女性汇总在一起的数字并不会产生误导。 [4]
衡量白人死亡率逆转现象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将实际发生的情况与虚线所示的趋势进行比较。这两条线之间的差距显示了实际与预计死亡率在每一年的差异,从中我们可以计算出,如果20世纪末的进步得以持续,在每年死去的45~54岁的美国白人中,有多少本来应该活在世上。如果把1999年(逆转开始的年份)到2017年的数字相加,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死亡率像预期一样持续降低,死去的中年美国白人中有60万人本该活在世上。这里可以看一个直接的参考数字,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开始流行以来,共有约67.5万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估计,将其扩展到其他年龄组,并将其归因于特定的原因,但目前这个数字可作为我们所研究主题的粗略估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当前面对的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观察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因为预期寿命对年轻人的死亡更为敏感,中年人口死亡率只有发生巨大变化,才能影响它。对白人来说,2013—2014年新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了1.2个月。在接下来的三年间,即2014—2015年、2015—2016年,以及2016—2017年,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整体下降。这些下降反映了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不仅是中年人的死亡率,但事实上,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年白人死亡率影响。预期寿命的任何下降都是极其罕见的。随着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我们走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自从193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死亡登记覆盖各州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还从未出现连续三年下降。 [5] 对于在此之前已经进行死亡登记的州而言,唯一的先例是一个世纪前,即从1915—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大流感期间。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场灾难。
要想着手了解这些死亡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首先寻找线索,看看死亡到底发生在哪里。纵观1999—2017年美国各州45~54岁白人死亡率的变化,我们会发现,除了6个州以外,其他所有州的死亡率都有所上升,其中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死亡率增幅较大。这些州的教育水平均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美国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中年白人死亡率显著下降,而这些州的教育水平都很高。
图2-2显示了更为详细的地域分布,上图和下图分别为2000年和2016年美国大约1000个小区块内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个小区块一般代表一个县,如果某县人口很少,则一个小区块代表了相邻几个县数据的总和。颜色较深的区块表明死亡率较高,因此如该图所示,在2000年,西部各州(加利福尼亚州除外)、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部各州的死亡率较高。到2016年,情况更加恶化并蔓延到新的地区,例如缅因州、上密歇根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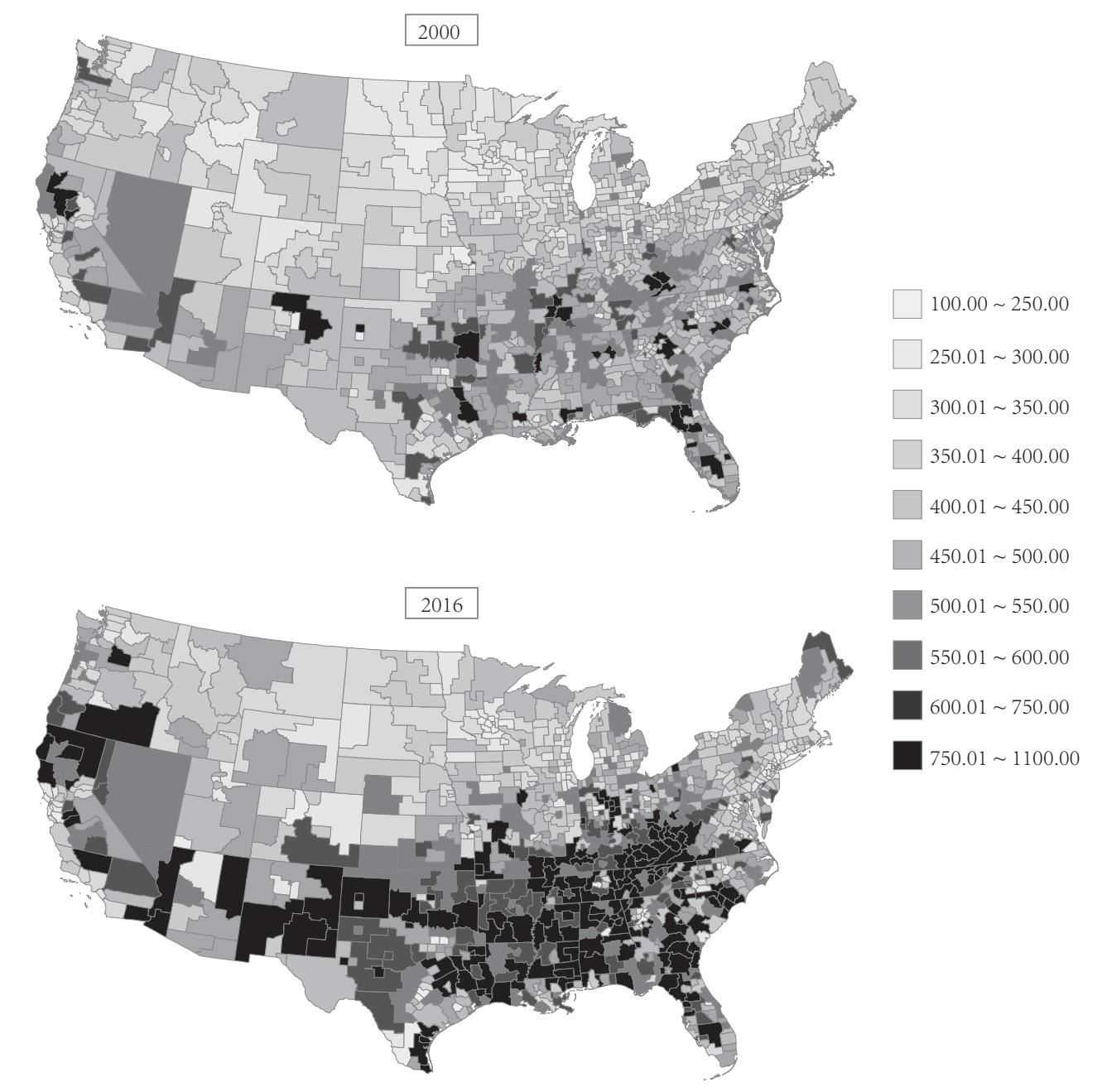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在本书后面的多个地方,我们将回顾这两张地图所显示的内容。
图2-1只是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特定年龄组(45~54岁)的死亡率,但我们关注的并非仅此而已。与其他富裕国家的情况相反,美国白人在整个成年年龄段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全部出现逆转。虽然我们强调了45~54岁的中年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死亡率上升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婴儿潮一代。对美国白人而言,他们在年轻时需要跨越的生存之栏也已经升高。
对今天的中年人来说,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那些成功活下来的中年人步入老年后能不能“走出”死亡危机的阴影?还是他们会带着满身烦恼逐渐老去,以至于我们会看到,明天的老人会像今天的中年人一样身陷痛苦?美国老年人享受的福利,例如通过医疗保险计划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通过社会保险计划提供的养老金,是中年人无法享受的,因此,如果这些福利对健康有益,今天的中年人将有一个乐观的未来。但是,如果1950年左右出生的人之所以出现中年死亡,是因为他们的长期生活条件或者因为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他们的情况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改善。不幸的是,最近的数据显示,事实更符合第二种较为悲观的预测。中年人死亡率上升的现象已经开始传染到老年组,因为二战后出生的人口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65~74岁的白人全因死亡率(各种原因导致的总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2%,但2012年以来,这一队列的死亡率已经停止下降。
社会学家经常试图分离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如果结果与年龄相关,可能存在年龄效应;另一方面,如果结果与出生在特定时期的人相关,并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一直伴随着他们,则可能存在队列效应。当然,队列效应与年龄效应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也不会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在此,我们倾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队列效应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很不幸,这种说法更为悲观。这群人身上存在一些特质,使他们容易受影响,并将伴随他们度过一生。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努力探寻那些特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审视两大类因素,它们通常被视为相互竞争的因素,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之一是外因或环境因素,它强调了人们的遭遇,他们所拥有的机会,以及他们所能获得的教育、职业或者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另一种则是内因,强调了人们的内在驱动力。换言之,它强调的不是人们拥有的机会,而是他们在面对机会时的选择,即他们自己的偏好。因此,这成为一场有关不断恶化的机会与不断恶化的偏好、价值观甚至道德感的辩论。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回到21世纪初的中年美国人身上,找出他们死亡的更多原因。毋庸置疑,自杀、阿片类药物滥用和酗酒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但这些绝不是全部。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7, Policy approaches to the opioid crisis, featuring remarks by Sir Angus Deaton, Rep. Ann McLane Kuster, and Professor Bertha K. Madras: An event from the USC- Brookings Schaeffer Initiative for Health Policy, Washington, DC , November 3, https:// www. 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11/es_20171103_opioid_crisis_transcript.pdf.
[2]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在整本书中,我们将非西班牙裔白人称为“白人”,将非西班牙裔黑人称为“黑人”,将所有种族的西班牙裔人称为“西班牙裔”。
[3] See Katherine Baicker, Amitabh Chandra, and Jonathan S. Skinner, 2005,“Geographic variation in health care and the problem of measur ing racial disparities,”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8(1), supplement (Winter), S42–53.
[4]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停滞或逆转是否部分由于这一中年年龄组人口在这段时间变老了。确实,1990—2017年,45~54岁年龄段的人的平均年龄增长了0.4岁(从49.2岁增加到49.6岁),而我们可以预见,死亡率也会由于平均年龄的增长(哪怕是小幅上升)而有所提高。不过图表已经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并进行了相应调整。如果不进行调整,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曲线还会稍高一些,但是美国白人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或者与假设20世纪末期的进步得以延续而本来预期可以达到的水平之间,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任何此类调整都无法消除这种差异,参见Andrew Gelman and Jonathan Auerbach, 2016, “Age- aggregation bias in mortality trend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13(7), E816–17。
[5] 本书交付出版之时,我们尚不知道2018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会有什么变化,目前也不清楚它将以何种方式变动。
贝基·曼宁:我丈夫的心里充满内疚,他认为我们的儿子吸毒全是他的错。然后,他开始变得特别沮丧,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保罗·索尔曼:他是怎么死的?
贝基·曼宁:他一枪爆头自杀,我正好回家,目睹了这一幕。
保罗·索尔曼:我最好的朋友玛西·康纳的丈夫也是自杀身亡的。
玛西·康纳: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酗酒。
保罗·索尔曼:他几个一辈子的好朋友也都嗜酒如命。
玛西·康纳:(那几个朋友中)一人虽然死于心脏病,但一生都身陷毒瘾和酒瘾。另一人死于癌症,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喝酒。我丈夫身上装了一个G管(胃造瘘管),他把酒倒进了管子,自杀了。 [1]
美国的中年白人到底死于什么?上面的对话摘录自肯塔基州的一次采访,这次采访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上播出,上面短短的几句话捕捉到了被我们称为“绝望的死亡”的三大原因,即自杀、药物和酒精。它还显示了这些原因之间的密切关系。贝基·曼宁的丈夫因为儿子吸毒而抑郁自杀。曼宁的丈夫和朋友在成年后长期滥用酒精和毒品,而玛西·康纳的丈夫则直接将酒精灌入自己的胃中自杀。他们的一个朋友死于心脏病,但酒精可能是间接死因,因为对那些长期患有心脏病的人而言,酒精会导致他们心脏病发作。
我们在初次看到图2-1的早期版本时曾自问,这些人到底死于什么。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以了解自1999年白人死亡率开始上升以来,哪一类死亡增长最快。我们发现了三大罪魁祸首。按重要性排列,它们分别是意外或故意(原因不确定)的中毒(几乎全是药物过量使用)、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其中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数量高于自杀或与酒精相关疾病的致死数量,但自杀和酒精加在一起杀死的白人则多于药物过量使用。这三个原因的死亡人数都很高。显然,死神继续着自己的旅程,它从儿童的胃肠道进入老年人的肺和动脉,现在又掉头回到中年人的大脑、肝脏和静脉。
上述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白人中急剧上升,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其他富裕国家里。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和澳大利亚,药物滥用致死人数比原来更多,在英国和爱尔兰,与酒精相关的死亡人数也有所增加(我们掌握的数据不支持将上述国家或其他富裕国家的死亡人数再进一步按照种族群体细分)。其他国家的此类死亡人数上升对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情况在未来可能变得更严重。但是,除了苏格兰的药物相关死亡之外,其他各国的数字与美国的数字相比微不足道。同时在美国,至少在2013年以前(芬太尼这一致命的阿片类药物恰好在那一年上市),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中均未出现绝望的死亡人数上升的情况。
尽管美国在某种传染病肆虐期间,也可能出现死亡人数激增,例如,1918年的流感大暴发,但这一次,致命的流行病并不是借助病毒或细菌传播的,也不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比如空气污染或核事故的放射性沉降物。相反,这些死亡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因酗酒而死,或过量使用药物将自己毒死,或者以开枪或上吊的方式自杀。的确,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这三种死因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验尸官或法医往往很难对死亡进行分类,区分自杀和意外导致的药物过量使用往往并不容易。所有死亡都是生活中巨大苦困的结果,无论是一时之苦,还是长期之困。因此,把所有死亡全部归类为自杀看上去也不无道理,无论这些人是用枪快速地杀死自己,还是将头颈伸入绳结,然后将脚下的椅子踢开,或者慢慢地用药物或酒精结束自己的生命。话虽如此,但许多瘾君子其实并不想死,即使他们心知肚明,死亡是他们染上毒瘾的必然结果。
绝大多数药物引发的死亡被归类为“意外中毒”,但这些意外事故与从梯子上摔下来或误触带电的电线完全不同。不可否认,死者中确实有些人是误服了错误剂量的药物,或者不小心给自己注射了身体无法承受的海洛因剂量,又或者误判了药物和酒精效果叠加的风险。但是,那些听说了附近发生“意外死亡”的瘾君子,还会去找毒贩,以确保自己也能获得高强度的毒品,我们对此该做何解释?还有一些人四处寻找芬太尼这种毒性比海洛因强很多倍,因而更危险的药物,对他们的行为又该做何解释?《华盛顿邮报》曾报道了阿曼达·贝内特的故事。26岁的阿曼达是巴尔的摩的居民,剖宫产后陷入阿片类药瘾,后来发展成服用海洛因,然后又发展为服用芬太尼和海洛因的混合毒品。她表示:“如果海洛因里面不加芬太尼,我根本不想要。” [2]
当然,寻找此类药物的人并不是在寻求死亡,他们要找的只是那种强烈的快感或者暂时的解脱,而这样做带来的高死亡风险并没有什么威慑力。有些瘾君子在过量吸毒后,因及时使用纳洛酮而奇迹般地被救了回来,但他们在几小时后又会过量吸毒。酒瘾不像阿片类药物上瘾那样会带来直接危险,而且生活中确实有一些高功能的酗酒者(虽酒精成瘾,但维持着良好的生活能力),正如同样有一些高功能吸毒者一样。但是,还有很多人因成瘾而失去家庭、工作,乃至生命。成瘾就像一座监狱,它将受害者与有意义的生活彻底分隔。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罗伯特·杜邦认为,成瘾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尽管使用某种物质导致了严重后果,但仍继续使用;二是不诚实。 [3] 如他所说,“自私的大脑”控制了一切,除了对成瘾之物的渴望之外,不给其他任何东西留有余地。 [4] 那些置身于酒精或毒品致命副作用危险的人,早已失去许多令生活有价值的东西,这与许多决定自杀的人经历的损失非常类似。
我们之所以将这三类死亡通称为“绝望的死亡”,是为了赋予其一个方便的标签,以表明它们与痛苦的关联,与精神和行为健康的联系,以及缺乏任何传染源的特点。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确定绝望的具体原因。关于绝望的背景原因,或“原因的原因”,我们有很多话要说。现在,它只是一个合适的标签。在45~54岁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中,因绝望而死的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92‰。在1999—2000年到2016—2017年,美国所有州45~54岁白人的自杀死亡率都有所上升,在除两个州之外的所有其他州,酒精性肝病的死亡率也都呈现上升趋势。 [5] 同样,在所有的州,药物过量使用的死亡率也在上升。
我们并非第一次见证药物滥用现象的增多。目前的流行病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6年,在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后,普渡制药公司生产的成瘾性处方止痛药奥施康定(实质上就是合法化的海洛因)开始上市销售,流行病的势头开始增强。与此同时,专门研究与酒精肝相关的死亡和自杀的学者也看到这些原因的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尤其是在中年白人当中,尽管这一点并没有像药物滥用死亡那样受到公众关注。我们的贡献是将药物滥用、自杀和酒精相关死亡联系起来,并注意到它们均在同步上升,共同折磨着许多白人,而且在这一群体中,总死亡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停止或发生逆转。我们还选择了“绝望的死亡”这个统一的标签,这样做有助于让人们了解这种综合性的流行病,并强调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药物过量使用。
卫生经济学家埃伦·米拉和乔纳森·斯金纳此前在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指出,虽然绝望的死亡人数确实在迅速上升,但仅凭它们的总数,尚不足以解释总体死亡率下降趋势的停滞或逆转。 [6] 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为何一改20世纪的下降趋势,并且在21世纪与美国其他群体和其他富裕国家分道扬镳,一定还存在别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所说的这些“别的原因”。
1970年后,美国的死亡率显著下降,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相应延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心脏病和癌症这两大杀手的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在75岁之前,死于癌症的风险高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在75岁之后,心脏病则会带走更多生命。因为老年人的死亡率最高,所以心脏病是美国的头号杀手。癌症则是美国中年人的头号杀手,而我们在治疗癌症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这一进展也延续到21世纪。但研究表明,和绝望的死亡共同导致中年人死亡率停止下降的“其他原因”,是我们在降低心脏病死亡率方面的进展明显放缓,而心脏病死亡率的降低,长期以来都是推动健康状况改善和预期寿命提高的引擎。以前在这一领域的进展通常被归因于人们开始戒烟,特别是男性开始戒烟,因为他们通常比女性更早戒烟,并且比女性更容易死于心脏病。此外,更多的人开始服用预防性药物(降压药和他汀类药物)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20世纪80年代,美国45~54岁的白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迅速下降,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下降的速度已经降为每年2%。在21世纪前10年,下降速度更是放缓至每年1%。虽然2010年后,这一比例又恢复上升势头。 [7]
图3-1显示了美国45~54岁的白人中,以及英国和其他讲英语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爱尔兰)死于心脏病的人数。1990年之后,如我们所期,随着吸烟现象减少和预防医学的普及——所有富裕国家都可以随时提供预防性治疗——死亡率稳步下降,并且各国的死亡率日趋相似。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它再次与其他富裕国家背道而驰。毫无疑问,心脏病防治的进展放缓是导致图2-1中“分道扬镳”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第二章中估计,45~54岁白人中有60万的“额外”死亡人数,这其中的15%源自心脏病,而不仅仅是绝望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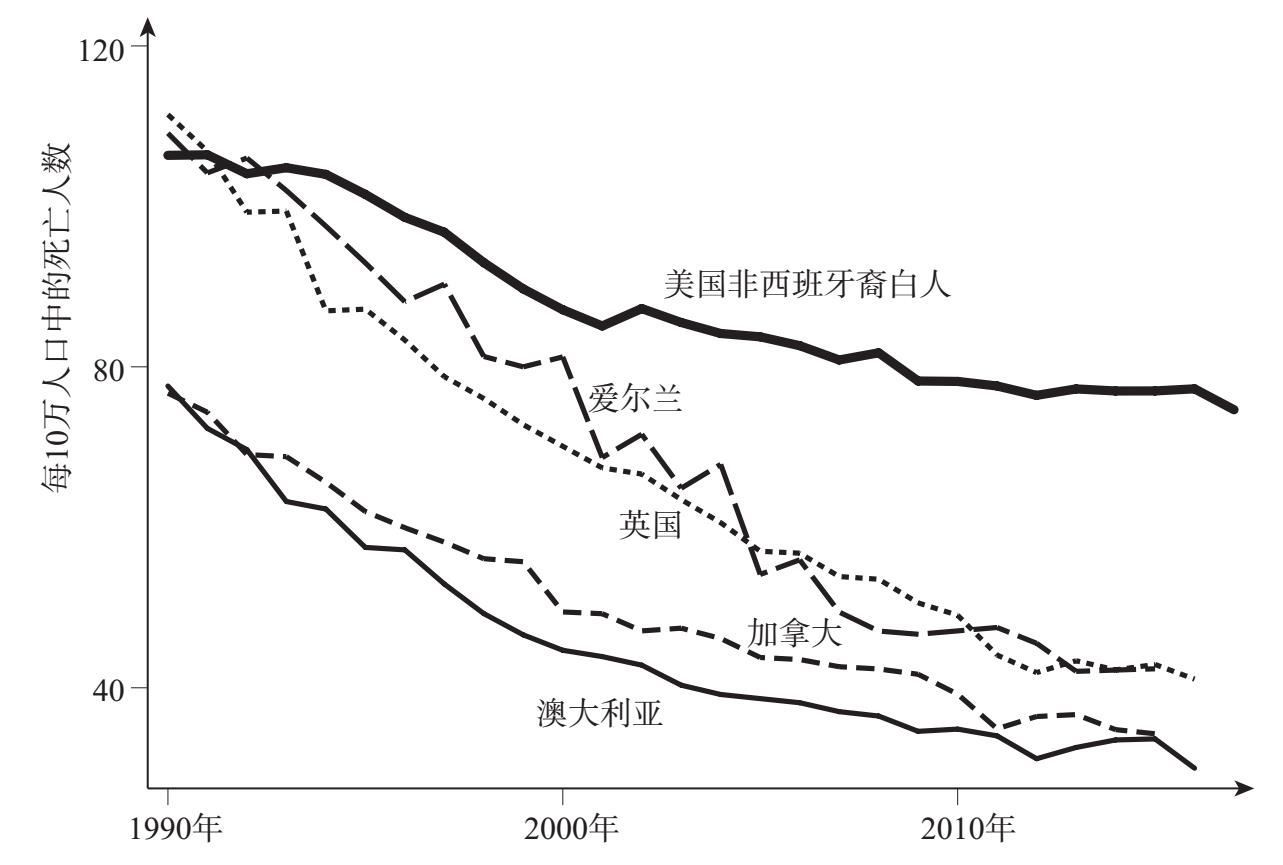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
2010年之前,其他讲英语国家的心脏病死亡率一直呈现强劲的下降走势,然而,这个趋势在2011年后突然结束。这一走势,即在2010年前稳步下降,但随后死亡率趋于平稳,同样出现在美国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之中。这使得讲英语的国家与其他富裕国家的情况发生背离,因为在其他非讲英语的富裕国家中,中年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仍然在持续下降。这也许是由于讲英语世界的预防性措施已经没有进步空间,也许是由于戒烟的人数已经达到极值。但这些都不能解释美国的心脏病死亡率为何表现得如此不佳。按照国际标准,1990年美国的心脏病死亡率相当高,因此其应该有更大的改善空间,而不是无所作为。
在研究药物过量使用或自杀现象时,死因的分类指向直接原因。但是,心脏病有多种形式以及很多潜在的原因,所以很难确定图3-1中死亡的具体原因。一种可能性是,与绝望的死亡相关的药物和酒精可能会使人们更容易死于心脏病。虽然有人认为,适度饮酒(女性每天饮一杯酒,男性每天饮两杯酒)会增加“好”胆固醇(HDL)和减少“坏”胆固醇(LDL)的影响,但长期大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并削弱心肌功能,从而导致心脏病。狂饮(一两小时内喝三杯或更多的酒)会刺激心脏不规律地跳动。鉴于不同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不同,药物滥用与心脏病的关系更为复杂。甲基苯丙胺和可卡因(被称为“完美的心脏病发作药物”)是兴奋剂,会增加血压和心率,从而使心脏病发作和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加大。人们目前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引起的心脏病风险知之甚少。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长效阿片类药物与心血管疾病死亡之间存在联系,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8] 如果有证据表明,长期酗酒或滥用药物会导致心力衰竭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那么这些死亡也可归类为绝望的死亡。
不过,吸烟、高血压和肥胖似乎是对中年期心脏健康更普遍的威胁。虽然在过去20年,美国的吸烟率总体出现下降,但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等中南部各州居民中),吸烟率仍然居高不下,同时某些人口群体中的吸烟率也持续上升(例如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白人妇女中)。近年来,坚持服用降压药的人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到目前为止,最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肥胖可能导致心脏病。美国人普遍超重,他们是世界上最重的人群之一,而且许多学者早就预测,肥胖人群的长期增加将破坏健康的进步,现在这种预测正在变成现实。许多研究都显示了肥胖的风险,包括其会导致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肥胖与糖尿病之间的联系特别紧密,而如果糖尿病患者同样患有心脏病,其死因通常会被记录为心脏病。 [9] 吃得过多,就像喝得太多一样,对一些人来说是面临压力时的反应,是他们在面对生活困难和失望时的自我安慰,因此与肥胖相关的死亡或许也可以被列为绝望的死亡。
我们在此并不想沿着这条路继续探索,部分原因是很难统计哪些因心脏病造成的死亡与暴饮暴食有关,但有关肥胖的阐述还远未完成。那些散布有关肥胖的悲观论调的人喊着“狼来了”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所预测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的时间,也远远早于实际出现任何此类迹象的时间。 [10] 此外,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与肥胖相关的风险在近年来有所降低,或者其在今天的风险已经低于进行风险研究时的水平。相关研究必须跟踪人们多年,而随着新的防治程序和药物不断出现,这些研究总是面临一个风险,即其在完成之前就已经过时。由于肥胖增加心脏病风险的途径之一是肥胖导致高血压,因此降压药物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就可能令肥胖者比以前更安全。
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也引发有关肥胖影响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尚未得到解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英国和澳大利亚45~54岁成年人肥胖率的上升与美国白人肥胖率的上升水平几乎相同, [11] 但是同期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心脏病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了4%。此外,2011年后美国黑人、西班牙裔人群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中年人心脏病死亡率的下降也出现停滞,这也留下一个疑问,即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无论其最终原因是什么,对美国白人而言,正是特立独行的心脏病死亡率模式与独有的绝望的死亡模式相结合,导致中年人死亡率在1998年之后止降回升。我们可以借助一场拔河比赛想象这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在绳子的一端,我们在对抗心脏病方面取得进展,因而降低死亡率;而在另一端,绝望的死亡则在努力拉拽(尽管最初的力道微弱),不断推高死亡率。1990年,心脏病防治的进展“占据优势”,从而使总体死亡率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脏病防治的进展日渐乏力,而绝望的死亡却“越战越勇”,于是总死亡率停止下降,并在一些中年群体中开始回升。
上面的类比对我们在这里的阐述非常重要,因为心脏病死亡率水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进展速度都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全因死亡率的拔河比赛在不同的年龄段呈现不同的结果。对于20多岁或30岁出头的白人而言,心脏病并不是一个主要杀手,在过去20年,这群人中绝望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一直在推高其全因死亡率。对于30多岁和40多岁的白人来说,心脏病和癌症发病率下降的影响以及绝望的死亡人数增加的影响一直势均力敌,直到2013年,由于更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出现,药物过量使用开始导致绝望的死亡人数加速上升。对于50多岁的白人来说,从新世纪开始,由于心脏病防治的进展彻底崩溃,完全无力对抗因药物过量使用、酒精和自杀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量增加,因此全因死亡率持续上升。
我们的叙事顺序遵循了我们发现这一切的方式,即从各种形式的中年死亡开始,然后关注导致这些死亡发生的直接原因,进而发现这是由于白人群体中存在绝望的死亡,再加上心脏病死亡率下降这一全因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引擎出现减速和逆转。不幸的是,绝望的死亡不仅折磨着中年白人。虽然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影响,但年轻白人因绝望而死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特别是药物过量使用和自杀导致的死亡人数。1990—2017年,在45~54岁的白人中,绝望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两倍。2017年,尽管这一中年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最高,但年青一代白人的表现也令人担忧,而且他们的死亡率上升速度更快,尤其是在过去几年,其绝望的死亡率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正如我们所写,这一流行病正在恶化。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提出一个有关这一流行病的观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年龄组都会比前些年同一年龄组的情况更糟糕。我们发现,中年组的死亡模式在近年一直向老年组蔓延。到2005年,中年组之外人群中的绝望死亡人数也开始增加。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本不该上演,这颠覆了正常的自然规律;孩子们应该安葬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反过来。子女的死亡,即便是一个成年子女死亡,也会撕裂一个家庭,而失去年富力强的人——那些本不该死去的人,也会颠覆社会和职场。在本章开头,我们看到了曼宁先生因无法面对儿子吸毒而自杀。今天,有数百万美国父母生活在恐惧之中,时刻担心某一天打给他们成年儿女的电话将无人接听,或者他们将接到警察或急诊室打来的电话。
[1] PBS Newshour , 2017, “‘Deaths of despair’ are cutting life short for some white Americans,” February16, video, 8:19, https:// www.pbs.org/newshour/show/deathsdespair-cutting -life-short-white-americans.
[2] Nicole Lewis, Emma Ockerman, Joel Achenbach, and Wesley Lowery, 2017,“Fentanyl linked to thousands of urban overdose deaths,”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7/national/fentanyl-overdoses/.
[3] Robert L. DuPont, 2008, “Addiction in medicin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Clinical and Climatological Association , 119, 227–41.
[4] Robert L. DuPont, 1997, The selfish brain: Learning from addiction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5] 在此期间,马里兰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酒精性肝病死亡率略有下降,而新泽西州则略有上升。许多小州几年未报告数据,如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在这些州中,除特拉华州外,数据报告期内的死亡率均有所上升。
[6] Ellen Meara and Jonathan Skinner, 2015, “Losing ground at midlife in Ameri c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12(49), 15006–7.
[7] 这些统计数据包含了非西班牙裔白人和西班牙裔白人,能够获得的1990年之前按种族划分的数据并不完善。
[8] Yulia Khodneva, Paul Muntner, Stefan Kertsesz, Brett Kissela, and Monika M.Safford, 2016, “Prescription opioid use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roke, and cardiovascular death among adults from a prospective cohort (REGARDS study),” Pain Medicine , 17(3), 444–5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281131/;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8, “Opioid use may increase risk of dangerous hearth rhythm disorder,” meeting report, poster presentation, November5, https://newsroom.heart.org/news/opioid-use-may-increase-risk -of-dangerous-heart-rhythmdisorder?preview=303c; L. Li, S. Setoguchi, H. Cabral, and S. Jick, 2013, “Opioid use for noncancer pain and risk of myocar dial infarction amongst adults,”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 273(5), 511–2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3331508.
[9] Andrew Stokes and Samuel H. Preston, 2017, “Deaths attributable to diabe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of data sources and estimation approaches,” PLoS ONE ,12(1), e017021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70219.
[10] Jay Olshansky, Douglas J. Passaro, Ronald C. Hershow, et al., 2005, “A potential decline in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352(11), 1138–45.
[11] For England, see NHS Digital, 2018, “Health Survey for England 2017,”December 4, https://digital.nhs.uk/data-and-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atistical/healthsurvey-for - england/ 2017; for Australia, se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2018, “Overweight and obesity rates across Australia 2014–15,” June7, https:// www.aihw.gov.au/reports/overweight -obesity/overweight-and-obesity-rates-2014-15/data.

★★★
★★★
在肯塔基州,就是贝基·曼宁和玛西·康纳讲述他们丈夫自杀故事的地方,2017年中年居民死于自杀、药物过量使用或酒精性肝病的风险比美国平均水平高1/3。但并非所有肯塔基亚人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只有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中,绝望的死亡的风险才明显上升。图4-1显示了肯塔基州45~54岁白人的绝望的死亡比例。1995—2015年,在获得了低于学士学位的人中,每10万人中的死亡人数从37例上升到137例,而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中,死亡率则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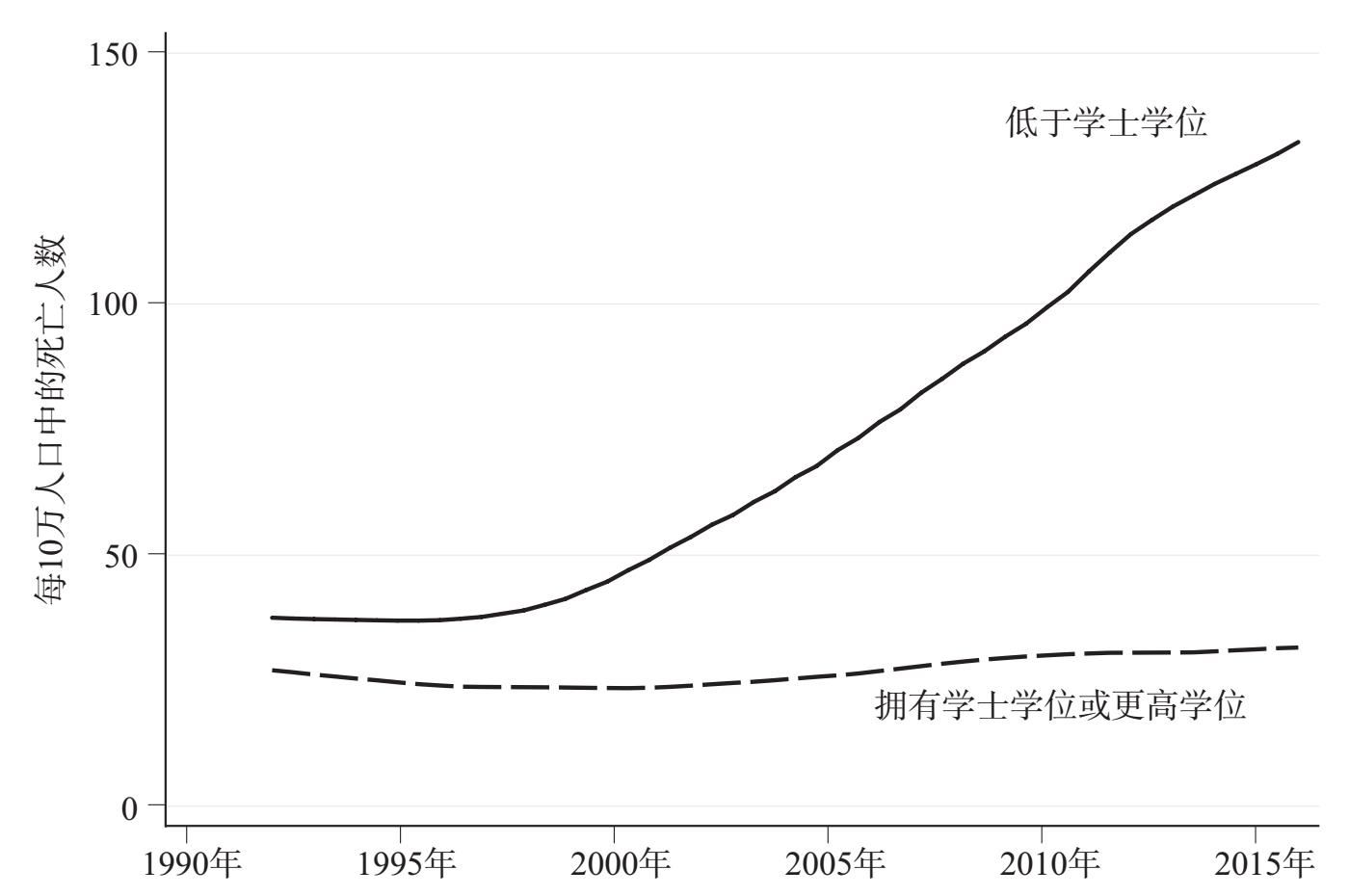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肯塔基州是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州之一,其45~54岁的白人居民中,仅有25%拥有学士学位。不过,美国所有州都存在类似的模式,即那些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死亡风险迅猛增加。受教育程度显然成为了解死者到底是哪个人群,以及他们因什么而死的关键因素之一。看上去,死神从动脉和肺到大脑、肝脏和静脉的巡游之旅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当中。如果想要了解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所面临的额外风险,我们就需要了解教育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2017年,在25岁以上的美国人口中,将近40%的人拥有的最高文凭是高中文凭,27%的人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但并未获得学士学位,33%的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在1925—1945年出生的美国人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20~24岁的成年人中只有10%接受了高等教育。到60年代末,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20%。 [1] 但自此之后,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45年出生的人口中,1/4持有学士学位。1970年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3持有学士学位,增长的比例极为有限。而在1970年后出生,应该于1990年后大学毕业的人口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增长。
上大学给人带来的最明显的好处是能赚更多的钱,而有更多的钱能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与只拥有高中文凭的工人相比,平均薪资高了约40%。到2000年,这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收入溢价”的指标翻了一番,达到天文数字般的80%。 [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那些接受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但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溢价相对较为平稳,只比拥有高中学历者的收入高15%~20%。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并且决定不上大学的人根本无法预知,到了世纪末他们将会面临如此巨大的损失。
由于许多以前不需要学士学位就可胜任的工作现在变得需要学位,那些没上过大学的人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上过大学的人的机会则正在增加。2017年美国的失业率仅为3.6%,创下历史新低,但在那一年,只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口的失业率几乎是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两倍。2017年,在25~64岁并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美国人中,84%的人处于就业状态,而只拥有高中文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中,仅有68%的人有工作。 [3] 美国就业者的收入通常在45~54岁达到高峰。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这个年龄段里只拿到高中文凭就离开学校的人中,有整整25%的人已经脱离就业大军,而这一比例在那些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中只有10%。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存在很大的争议,到底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根本不想工作,至少是不想接受能付给他们当前工资的工作,还是他们其实希望工作,但却不能为之,因为没有工作提供给他们,或因为他们是残疾人。不管答案是什么,下列事实不容辩驳,那就是劳动力市场正在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机会,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则并非如此。
随着企业和政府不断应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加上计算机的使用大量增加,对更高技能和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与较高的人口之间,收入和就业差距会不断加大。对于少数幸运而有才华的顶尖人士而言,比如对冲基金交易员、硅谷企业家、首席执行官、顶级律师或医生,他们获得高薪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从前。2018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高达1720万美元,是人均收入的278倍。1965年,前者还仅为后者的20倍。 [4] 如果我们回到100年前,那时收入最高的人依靠的都是资本,他们是祖先财富的继承者。对于食利阶层来说,以工作为生是一种耻辱。没有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制造业从业者更丢脸的事了。如今,最高的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继承的财富,而是高薪收入(如那些首席执行官),或者创业及专业工作获得的收入(如咨询顾问、医生和律师)。教育,而非家庭或出身,是获得此类工作的必经之路。 [5]
人们在寻找另一半时倾向于选择有相似兴趣和背景的人。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有可能嫁给同样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曾经有一个时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会安于做家庭主妇,但在20世纪后期,她们已经走出家门,步入职场。因此,随着劳动力市场给予学士学位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以及更多高薪职业岗位向女性开放,我们开始看到更多对双方都拥有高薪收入的夫妻。换言之,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已经不仅是一份高薪工作的入场券,还是夫妻双方均拥有高薪的婚姻的入场券。
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将在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割裂。 [6] 在工作方面,如今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教育隔离”。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现在,大公司正在将许多过去由内部雇员完成的低技能工作外包出去。过去,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会一起工作,都是同一家公司的雇员。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居住的地点相互隔离,那些成功者居住在房价高企的地方,不那么成功的人根本无法进入。由于地理隔离加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孩子所上学校的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成功的夫妇除了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之外,几乎没有时间参与其他社区活动,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互认识,了解彼此关心的事情,或者共同参与社区活动。这两类人的品位不同,他们在不同的餐馆吃饭,访问不同的网站,看不同的电视频道,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新闻,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读不同的书。正如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依恋也大不相同,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结婚较晚,但更不容易离婚,他们生孩子的时间也较晚,拥有非婚生子女的可能性也较小。
盖洛普公司在美国人中做过一个大样本调研,要求受访者将他们的生活从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生活)到1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进行打分。2008—2017年,超过250万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打出的平均分是6.9分。那些拥有学士学位及更高学位的人打出的平均分为7.3分,只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打出的平均分为6.6分。在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原因中,只有大约一半与他们拥有更高的收入相关,从而表明这种较高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本身带来的巨大优势,或者至少要归因于教育带来的非收入性益处。盖洛普调查还询问人们是否每天都能做一些有趣或喜欢的事情,在此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同样具有巨大的优势。 [7]
一个总体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会大有不同,而且这些不同将会远远超越个体的差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受益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的创新能力和更高的生产力。更好的机会平等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赞成向那些曾经因家庭、收入或出身而被排斥在外的聪明孩子开放教育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制度是宛如试金石一样的美德,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成功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没有人会怀疑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事实上,在某些领域,我们显然还需要更多地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一个绝佳的例子是看看哪些人会成为发明家。发明是经济增长和未来繁荣的关键。与出身于收入分配后50%家庭的孩子相比,出身于在收入分配中位于前1%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0倍。精英制度的失败会导致我们错失未来的“爱因斯坦”,而他们本来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8]
当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制度也有缺点。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并预言其兴起将引发一场社会灾难。 [9]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曾经对非大学毕业生开放的工作现在只留给有学士学位的人。如果那些有学位的人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比如执法部门的工作,这本身无疑是一件好事。但鉴于有些资源的供给有限,比如良好的生活和工作场所,这意味着有些资源将不会再分配给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最严重的一点,也是杨担心的一点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将失去他们中最聪明的一批人,从而让他们失去本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人才。杨写道:“就国民支出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实质上是一场智慧之争,如果一个群体中最聪明的一批人投身敌营,那么这个群体将毫无胜算可言。”他指出,精英相对于其他群体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真正的原因是,“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已经无人再为卑微者代言”。如果有才能的人没有机会向上走,他们将无缘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并在那里出类拔萃和造福他人。但如果人才向上流动,则会损害他们的出身之所,以及他们原来所在群体的利益。杨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称为“民粹主义者”,把精英称为“伪善主义者”。 [10]
在上述论断提出60年后,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撰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并讨论了精英制度的腐蚀性影响:“成功者受到鼓励,认为自身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将其视为一种美德,并瞧不起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而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则可能抱怨整个系统受到操控,赢家是通过营私舞弊迈入成功之道的。或者,他们可能会心怀沮丧,认为失败全是自己的错,完全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和追求成功的动力。” [11] 根据201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学对国家有积极的影响,59%的共和党人(这个党派已经越来越成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支持的政党)认为大学正在造成负面影响。 [12]
因为精英的选拔依据是个人能力,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或地位,所以这些人显然比其所取代的那群人更有能力。同样,这种机制在许多方面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当一个新的群体获得成功后,它就会走之前群体的老路,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对抗下一代的精英。他们的能力越强,就越能成功地为自己和孩子制定排除异己、谋取私利的策略。虽然这些策略有助于个人获得利益,但对整个社会具有破坏性。富人们会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获得高水平大学的入学申请和相关文书的辅导,甚至会寻求子女存在精神障碍的诊断,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继续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先修课程的学习和考试。 [13]
当精英制度像其在今天的美国那样,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同时,那些已经得到公认的成就(如考试通过、晋升、成为合伙人、投机成功或当选公职)能够得到巨大的回报,那么这些回报可能不仅仅源于个人的能力和美德,还可能源于作弊,以及无视那些长期存在却已被逐渐视为成功障碍的道德约束。“如果没作弊,你就是没努力”的说法不仅仅适用于体育运动,在一个不平等的精英制度下,公共行为的标准很可能非常低,一些精英成员会做出腐败行为,或者他们在圈外人的眼中十分腐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9年美国大学的入学丑闻,即有钱的父母为了确保孩子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而行贿。我们猜测,在当今美国极度不平等的环境中,精英制度的兴起已经促成企业界呈现“赢者通吃”和更为严酷的氛围。 [14]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制度最终将自己走向灭亡。 [15]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的死亡率较高,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防范可预防疾病方面,教育之所以能够对人们提供保护,是因为了解疾病的运作机理有助于人们防范这种疾病,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了解这些信息。人口统计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和迈克尔·海恩斯已经证明,20世纪初,在病原菌学说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之前,“医生子女的死亡率与普通孩子不相上下,这相当清楚地表明,医生的手上几乎没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来提高生存率。到1924年,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已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5%。教师子女的进步也非常迅速,在此期间同样取得长足进步的还包括所有专业人员群体”。 [16] 再往后看,在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发布关于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报告之前,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吸烟率非常接近。但在此之后,不同群体的吸烟率开始出现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戒烟率更高,最初的吸烟率也更低。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下面的现象,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仍然保持较高的吸烟率。知识显然不是万能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模式,这一点经常被发现,也许社会地位本身是理解这些行为的关键之一。 [17]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的健康行为也不一样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2017年,审视不同群体中的吸烟者比例,我们发现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成年美国白人(25岁及以上)群体与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群体相比,前者中吸烟者的比例高达后者的4倍(29%与7%),接受了某种形式的大学教育,但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群体中的吸烟者比例介于两者之间(19%)。2015年,在只拥有学士学位以下文凭的白人中,1/3的人肥胖,而在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这一比例不足1/4。此外,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在控制高血压方面也表现欠佳。那些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与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相比,平均身高也高了大约1.3厘米,这反映出前者在童年时期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好。 [18]
这些因素导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象,即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群体中,死亡率的差距迅速扩大。整体来看,45~54岁年龄段的白人的死亡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不变,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没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口的死亡率上升了25%,而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了40%。 [19] 2017年,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口的收入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两倍,这说明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生活中有一定优势。同时,他们在中年死亡的风险只有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的1/4,这说明了他们在健康方面的优势。
虽然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差距的加大也加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死亡率的差距,但在只有低于学士学位的人口中,绝望的死亡人数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因死亡率差距的扩大。图4-2显示了美国的总体情况,并分别列出了男性和女性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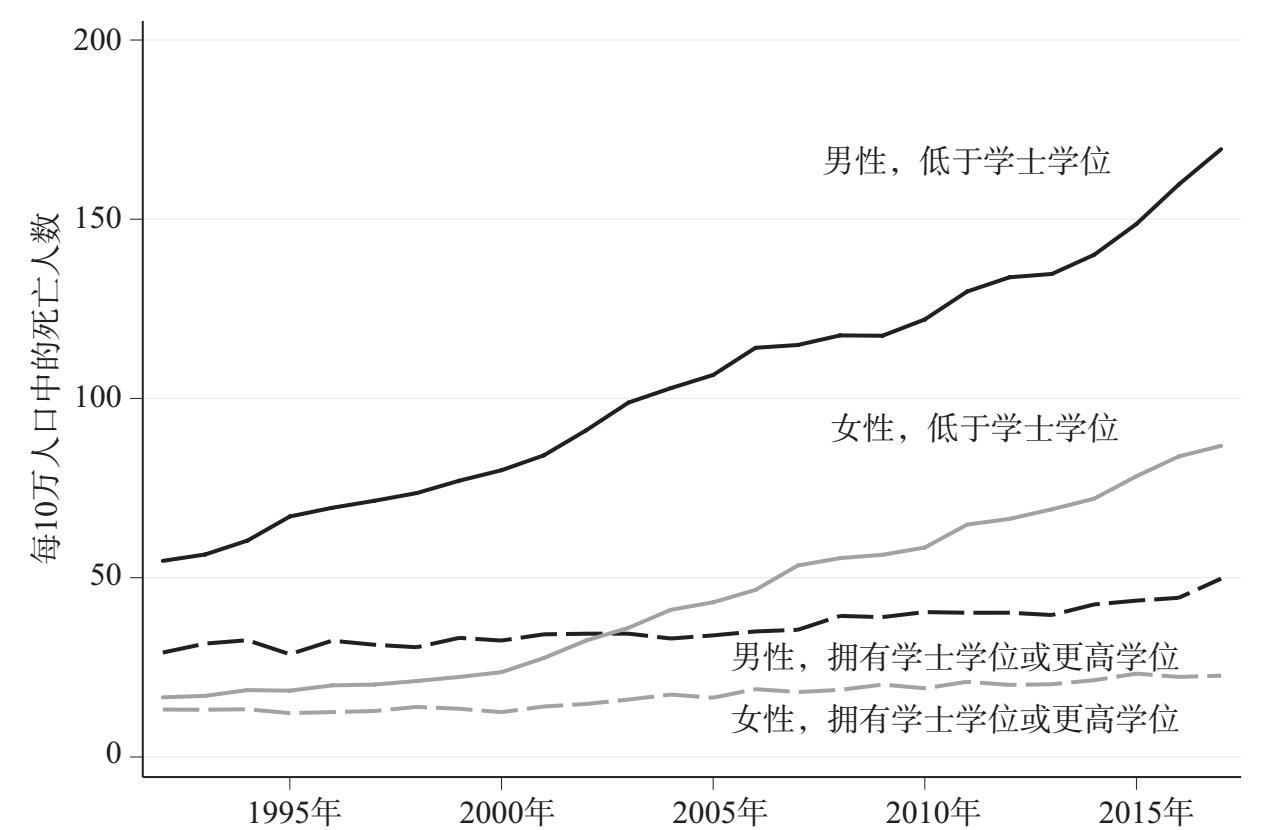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根据年龄组内平均年龄的增长进行了调整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女而言,如果拥有学士学位,他们出现绝望的死亡的可能性要比其没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低很多。1992年,男性中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死于酒精、药物或自杀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绝望的死亡“流行病”泛滥,这个差距也迅速扩大,到2017年,相对于拥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因绝望死亡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三倍。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白人妇女死于酒精、自杀或药物过量使用的风险都很低。早期媒体在报道我们的研究时经常会冠以“愤怒的白人男性不断死去”的标题,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女性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长期以来,女性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女性自杀的可能性较小,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世界各地似乎都是如此。同时,女性死于酒精性肝病或药物过量使用的可能性也较小。然而,图4-2显示,当前的这一流行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几乎相同。分别核实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三大因素后,我们发现这个诊断对各个因素也都成立。因此,我们不赞成一些人在媒体上鼓吹的观点,即这种流行病对妇女影响更大,这场“瘟疫”并没有什么性别歧视。 [20]
图4-3描绘了所有成年人,而不仅仅是中年人的绝望的死亡。在本图中,我们分别按照不同的出生年份研究了那些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跟踪不同出生队列随年龄增长的死亡率变化。花时间了解这些数字是值得的,因为这对于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还因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使用类似的数字。不同美国人的命运取决于他们何时出生,何时完成学业,以及何时开始工作,本书中的图能帮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信息。
左图显示了没有学士学位群体的情况,右图显示了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群体的情况。左图中的线条更容易看清,尽管两图的构图方法完全相同。图中每条线均代表一个特定的出生“队列”,即某一年出生的人群(在其上方以数字标明)。最左边的线代表了1985年出生的队列,最右边的线是1935年出生的队列。横轴表示的是年龄,每条线代表了各个出生队列在26年中(1992—2017年)的死亡率变化,这是我们掌握的数据能够支持的周期。为了使数字清晰可见,我们只摘取了每隔5年的一个出生队列。图中的每条线或“轨迹”都显示了绝望之死的死亡率是如何随着各队列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
通过研究越来越年轻的没有学士学位队列的死亡率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年轻队列的绝望的死亡的风险比年长的队列要高。对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同样在45岁时,1960年出生的队列面临的风险比1950年出生的队列高50%,而1970年出生的队列面临的风险则是1950年出生队列的两倍还多。出生越晚,在任何特定年龄遭遇绝望的死亡的风险就越高。除了年龄最大的队列(1935年和1940年出生的人),其他队列的死亡风险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每个队列面临的死亡风险因年龄增大而加剧的情况都比其前面一组人更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学士学位人口队列的情况与没有学士学位人口队列的情况大相径庭。与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不同出生队列所呈现的巨大差异)相比,右图中各个出生队列的死亡率轨迹很难区分。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一样,绝望的死亡的风险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至少在60岁之前是这样,但每一组人似乎都在沿着相同的轨迹变老。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同队列之间存在(相对而言极其微小)的差异,并且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出生较晚的队列同样表现较差。但是,以人口统计学的语言来说,这里没有或只有微小的“队列效应”,每个队列都遵循相同的老龄规律。
对于非西班牙裔黑人而言,无论其受教育程度较高还是较低,不同出生队列的死亡率模式都非常类似于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即在同等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但出生队列之间的差异很小。对黑人来说,年轻队列的情况并没有逐渐恶化。
对于1935年出生的非西班牙裔白人而言,图4-3显示了他们在六七十岁时的情况,他们中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绝望的死亡的风险并没有多大差异,只有十万分之三。但是,这种差异在后来出生的队列中急剧扩大,因此,在1960年出生的队列中(图4-3显示了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情况),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队列之间,遭遇绝望的死亡的风险的差异已经达到1935年出生队列的10倍。显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正面临一场灾难,并且出生越晚的白人面临的灾难越大,但这种灾难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则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
回到19世纪,甚至在埃米尔·杜克海姆于1897做的关于自杀的基础研究之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自杀。 [22] 在1935—1945年出生的队列中,自杀现象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中同样普遍。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队列开始,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在后面出生的队列中,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自杀风险的分化不断加大。对于1980年出生的人来说,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自杀的可能性是有学士学位白人的4倍。这些发生于21世纪的自杀与过去的自杀不同,它们发生在不同的群体中,同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导致其发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1] Statistics are from Thomas D. Snyder, ed., 1993, 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tatistical portrait ,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ble 3, https://nces. ed .gov/pubs93/93442.pdf.
[2] 收入溢价的计算方法是:拥有学士学位的全职、全年工作劳动者的时薪中位数,与只拥有高中文凭并没有接受额外教育劳动者的时薪中位数之比,参见Jonathan James, 2012, “The college wage premium,” Economic Com mentary , 2012-10,August 8,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3] 统计数据针对平民人口,参见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7。
[4] Lawrence Mishel and Julia Wolfe, 2019, “CEO compensation has grown 940%since 197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14, https:// www.epi.org/publication/ceocompensation -2018/.
[5]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8(1), 1–39; Thomas Piketty,2013,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2019, “Cap it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4), 1675–745.
[6] Robert D. Putnam, 2015,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 Simon and Schuster; Charles Murray, 2012,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 ca, 1960–2010 ,Crown; Sara McLanahan, 2004, “Diverging destinies: How children are faring unde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 raphy , 41(4), 607–27.
[7]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盖洛普追踪民调结果。
[8] Alex Bell, Raj Chetty, Xavier Jaravel, Neviana Petkova, and John van Reenen,2019,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 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2), 647–713.
[9] Michael Young, 1958,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 Thames and Hudson.
[10] Young, 152.
[11] Michael Sandel, 2018, “Popu 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open Democracy, May9, https:// www.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democracy/.
[12] Kim Parker, 2019, “The growing partisan divide in views of higher education,”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19, https:// www.pewsocialtrends.org/essay/the-growingpartisan -divide-in-views-of-higher-education/.
[13] Dana Goldstein and Jugal K. Patel, 2019, “Need extra time on tests? It helps to have cash,” July 30, New York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30/us/extra-time504-sat-act.html.
[14] Christopher Hayes, 2012, Twilight of the elites: Ameri ca after meritocracy ,Crown.
[15] See also Daniel Markovits, 2019, The meritocracy trap: How Ameri 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 ,Penguin.
[16] Samuel H. Preston, 1996, “American longev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yracuse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Policy Brief No. 7, 8; Samuel H. Preston and Michael R. Haines, 1971, Fatal years: Child mort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 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 Michael Marmot, 2004, The status syndrome: How social standing affects our health and lon gevity , Times Books.
[18]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行为风险因素监视系统和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
[19] 对于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我们仅能追溯到1992年。从那时起,大多数州才开始在死亡证明上标注死者的受教育程度。但佐治亚州、俄克拉何马州、罗得岛州和南达科他州这四个州的标注工作进展较慢,因此我们所有的死亡和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都排除了居住在这些州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
[20]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7年,拥有学士学位的45~54岁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几乎保持不变,约为1/3。如果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学士学位和无学士学位人口的比例发生巨大变化,则将引发如下担心,即图中显示的不是死亡率变化,而是有学位和没学位的人口变化。人口比例的稳定使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21] 右图中,英文原书即无1950年队列,疑遗漏。——编者注
[22] Emile Durkheim, 1897, 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 , Germer Baillière; Matt Wray, Cynthia Colen, and Bernice Pescosolido, 2011,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37, 505–28.
《杜恩斯伯里》漫画的某期以B. D.和他的朋友雷为主角,雷声称黑人和拉丁裔群体之所以对绝望的死亡免疫,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痛苦和失去。B. D.讽刺地称这种免疫力为“黑人的特权”。 [1] 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正如中年黑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特权一样,他们在面对死亡的风险时也没有任何特权。
在过去25年里,至少直到2013年,非洲裔美国人并没有像我们在白人人口的记录中看到的那样,出现绝望的死亡的人数暴增的情况。不过,在更早一些的20世纪,由于霹雳可卡因和艾滋病的泛滥,黑人早已遭遇一场死亡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低技能黑人工人大规模失业之后。内城区的制造类和交通类工作纷纷消失,导致了社会动荡和大批人口失业,以及家庭和社区生活解体。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看到的那样,这个故事与过去25年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经历的一切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劳动力市场向不利于那些拥有最低技能的工人转变时,黑人首先出局,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水平低,部分是因为长期存在的歧视现象。几十年后,长期受到白人特权保护,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成为第二批受到打击的对象。在两个故事中,有关危机的起因的争论也非常相似,一方认为由于缺少机会,另一方则认为由于道德沦丧。因此,几十年前在黑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与今天白人的遭遇相比,或许更多只是时间不同,而不是本质不同。
我们将更详细地对此加以阐述,但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先从数字开始。

资料来源:Doonesbury © 2017 G. B. Trudeau.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Andrews McMeel Syndi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5-1显示了1968年以来,45~54岁的黑人和白人群体的死亡率。 [2] 黑人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白人,不过他们死亡率的绝对值一直高于白人。这种情况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当时黑人的中年死亡率与白人相比,达到令人震惊的2.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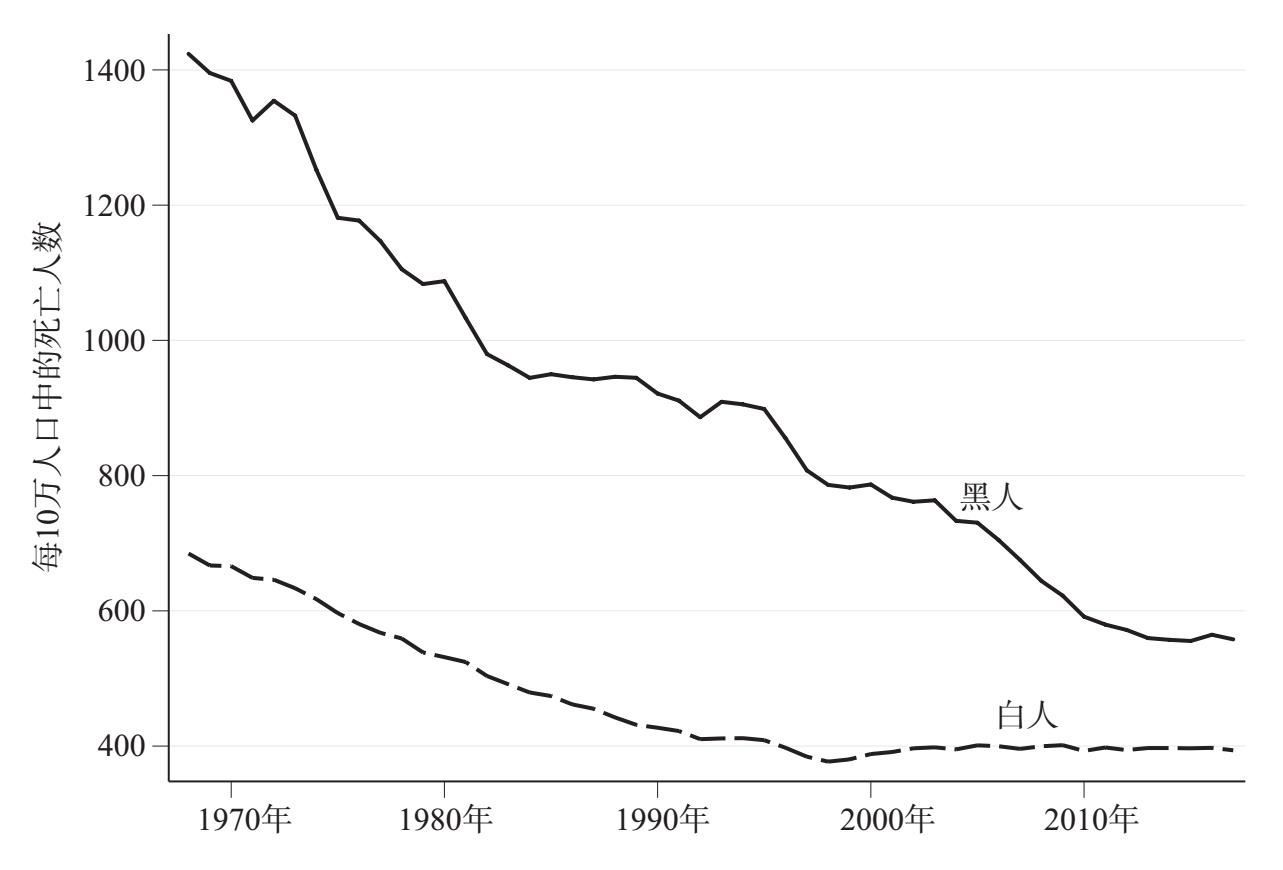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虽然黑人和白人死亡率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在不同时期,这种缩小的速度不同。20世纪60年代末,白人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因吸烟而停滞,使这一差距迅速缩小。到20世纪80年代,则轮到黑人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出现停滞。这一时期,黑人社区面临严重的艾滋病疫情。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讨论这部分内容。
从1990年起,黑人死亡率恢复下降势头,因此,当白人死亡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停止下降后,二者的差距又迅速缩小。虽然黑人与白人死亡率差距缩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如果这更多地源自黑人死亡率的下降增速,而不是因为白人死亡率的下降停滞,无疑将更令人欣喜。在图5-1的最右侧,黑人的中年死亡率也开始停止下降并掉头上升,我们随后也将对这一点再次进行讨论。
图5-1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图中反映的整个周期内,黑人的死亡率持续高于白人。总体而言,黑人的境况比白人更差。如果单纯比较死亡率的下降速度,黑人的速度快于白人,因此有人可能会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认为黑人比白人“做得更好”,即使他们的绝对死亡概率更高。我们将始终尽最大的努力非常清楚地区分我们谈论的是死亡率水平还是死亡率的变化(进步)。根本而言,死亡率水平,而非其变化率,对人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死亡率上,白人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即使白人死亡率上升,白人和黑人死亡率之间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2017年,黑人死亡率仅仅比白人在40年前的死亡率略低。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前面的漫画里B. D.会觉得奇怪,从所有衡量健康的指标(无论是变化率还是总体水平)来看,居然不是黑人的生活质量更差。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对生活某一方面权利的剥夺通常伴随着对其他方面权利的剥夺。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通常伴随着这些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在美国,黑人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更不可能拥有学士学位,并一直遭受歧视。因此,在黑人全因死亡率下降之时,白人的死亡率却在上升,这一点确实既不寻常,又令人惊讶。
21世纪初期,黑人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之所以快于白人,其主要原因是黑人没有遭受药物过量使用、自杀和酗酒流行病的侵害。
图5-2显示了1992—2017年,在45~54岁的白人(黑线)和黑人(灰线)中,出现的绝望的死亡数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是否拥有学士学位对死亡率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将黑人和白人按照是否拥有学士学位进一步区分为两个队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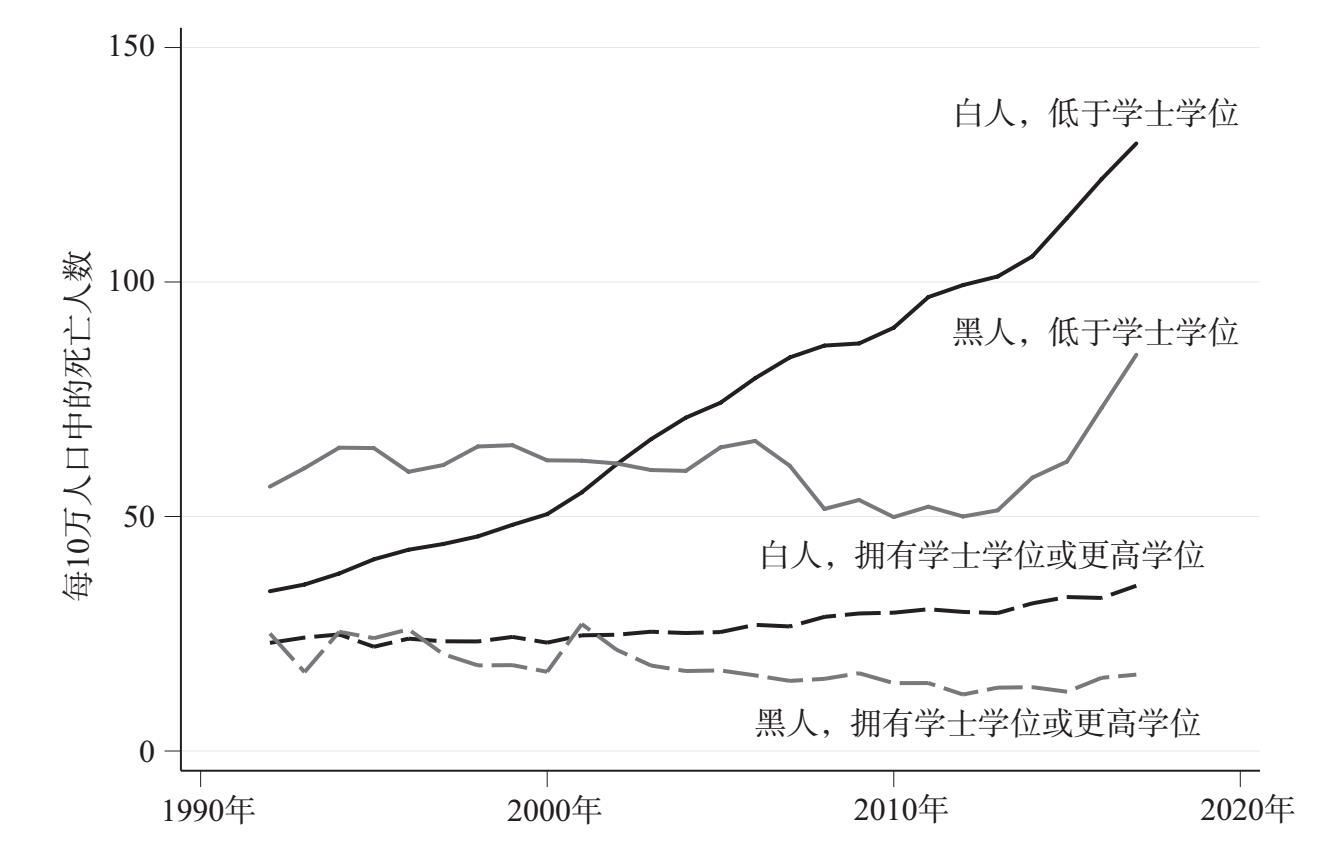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45~54岁年龄段(按年龄调整)
无论有没有学士学位,黑人中年的绝望死亡率在25年内均持平或下降,同期白人的死亡率则有所上升,特别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是否拥有学士学位对死亡率的影响均非常显著。
最近几年,黑人的死亡率也开始逐年上升,这是目前的阿片类药物泛滥与黑人社区早期的毒品泛滥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中探讨的,当前的药物过量使用流行病是由芬太尼引发的。芬太尼作为一种阿片类药物,比海洛因毒性更强,也更加危险。此前在黑人中流行的毒品使黑人社区拥有大量长期吸毒但社会功能稳定的瘾君子。然而,随着毒贩开始将芬太尼与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这些长期吸毒的瘾君子开始死亡。这些瘾君子并不知道,原本安全的剂量用在混合毒品上会变得致命。从黑人全因死亡率的低点(2014年)开始算起,涉及合成毒品(例如芬太尼)的死亡率上升是导致45~54岁黑人中年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在这些增加的死亡案例中,大约一半涉及合成毒品与海洛因的混合使用,另一半涉及与可卡因的混合使用。此外,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心脏病死亡率之所以停止下降,也可能与药物致死有关。不过,在上述情况出现之前,现行的流行病仍然是白人间的流行病。
无论是在前些年黑人的死亡流行病中,还是在目前白人的死亡流行病中,与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肝相关的死亡数字都相当高。但自杀死亡率在这两场流行病中不太一样,相对于白人美国人来说,非洲裔美国人自杀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黑人的中年自杀率在过去50年里变化不大,目前大约是白人自杀率的25%。这个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年龄而变化,但黑人的自杀率大大低于白人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早在1897年,埃米尔·杜克海姆就在他有关自杀的基础性研究著作中提到过这一点。 [3] 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尚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乔治·辛普森在为杜克海姆著作的英译本写序时,曾总结了杜克海姆的观点,即“系统的压迫和相对贫困,迫使个体适应了我们每个人必然面对的苦难和悲剧” [4] 。他还指出另外一点,而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有意义,即黑人较低的自杀率表明,相对贫困本身并不是自杀的原因。
我们认为,20世纪中叶后,内城区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预示了21世纪发生在白人身上的一切。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于1987年出版的《真正的穷人》一书中,讲述了更早的那个故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内城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受雇于制造业和交通业等“旧经济”产业。随着战后国际竞争加剧,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以及城市从制造业中心向行政管理和信息处理中心演变,非洲裔美国人在他们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遭受了巨大打击。他们的故事中充斥着失业和社会解体。据威尔逊所述,生活在城市里的黑人受雇的主要领域“在面对一些变化时极为脆弱,如结构性经济变化,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化为低工资部门和高工资部门,以及技术创新和制造业迁出中心城市” [5] 。面对这些变化,加之《公平住房法案》的通过,受教育程度更高和更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开始搬离内城区,留下越来越呈现一系列社会病态的社区,包括黑人家庭的逐渐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和暴力。
妇女因缺乏可结婚(有工作的)伴侣而未婚先孕,然后非婚生子。正如迈克尔·杨更早预测的那样,社区逐渐失去最有才华和最成功的人,这些人纷纷搬离内城区。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来说,一系列民权法案的通过也推动出现这种现象。曾经的内城社区包括专业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即同时拥有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人,但这些社区不但逐渐失去了成功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逐渐失去有工作的人。这对社区,特别是对社区中的年轻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威尔逊将内城黑人社区面临的问题归因于“劳动力市场大范围的有害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聚集和这些地区与较富裕黑人社区的隔离” [6] 。在谈到今天出现的类似现象时,经济学家拉格拉迈·拉詹曾指出,富有才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正不断向飞速成长和成功的高科技城镇聚集。 [7]
20世纪8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内城社区经历了一场霹雳可卡因危机。霹雳可卡因的泛滥与目前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既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霹雳可卡因非常便宜,并且能够迅速带来快感,人们非常容易上瘾。由于那些瘾君子急需钱,以获得下一次快感,所以犯罪率不断上升。随着毒贩们为争夺街角的一席之地而争斗,年轻黑人的死亡率激增。尽管目前仍有人买卖霹雳可卡因,它仍然在为害一方,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霹雳可卡因的流行热潮已基本消退。人们对其为何会消退仍存在争议,但下列原因起到了一定作用,即曾经迷恋霹雳可卡因的人逐渐变老,以及年青一代因为目睹它破坏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生活而对其心生厌恶。近期的研究表明,霹雳可卡因依然阴魂未散,它永久性地增加了内城区的枪支数量。 [8] 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曾经的泛滥也导致滥用芬太尼死亡率的上升。
某种流行病之所以泛滥,往往有深层次的原因,而不仅仅因为直接诱因。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内城区随处可以买到的霹雳可卡因,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白人社区中越来越多的阿片类处方药物,一概如此。导致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根源,是面向劳工阶层的工作永久性消失了,正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北部城市中的黑人,以及更近期美国各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所经历的那样。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员工医疗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企业大量削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数量,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黑人,随后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
在这两种流行病中,能够缓解心理或生理痛苦的药物以(相对)负担得起的价格摆在了那些渴望逃离的人群面前,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急需的避难所。在霹雳可卡因流行期间,内城区几乎没有任何合法的上升通道。同样,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轮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不到光明的经济前景或者生活方面的光明前景,于是他们正成为药物、酒精和自杀的牺牲品。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比较曾经的黑人和今天的白人时。绝望的死亡中包括自杀,而自杀率在不同种族中存在显著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不幸遭遇源于黑人文化的失败。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从1977年至2001年一直是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他还曾担任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顾问。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黑人家庭》 [9] 。在报告中,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核心问题是缺失父亲的家庭,并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奴隶制。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也在《失去的基础》一书中提出,这种社会病的根源并非缺乏机会。他还提出一个观点,即那些旨在对抗贫困的福利政策正在产生破坏作用,并助长懒汉行为。默里在其新书《走向分裂》中,将当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的许多问题归因于自身的道德沦丧,尤其是勤奋精神的丧失,即人们不再对谋生或养家糊口感兴趣。 [10]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并将证明默里的文章无法解释最近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身上发生的一切。如果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工资应该上涨,但是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工资水平和就业人口数量同时下降。这清楚地表明,问题的根源是工作需求下降,而不是供给下降。对于较早发生在黑人身上的故事,我们支持威尔逊的观点,即“有关贫困阶层生活和行为的保守论断不够有力,因为它缺乏直接证据,并且它们似乎互为因果。换言之,它们通过对贫困阶层行为的解释推导其文化价值,然后又以这些价值解释贫困阶层的行为” [11] 。
[1] Gary Trudeau, 2017, Doonesbury , Washington Post , March 26.
[2] 死亡率是所有白人(包括西班牙裔白人)和所有黑人(包括西班牙裔黑人)的死亡率。1968年之前,死亡证明将死者归类为“白人”和“其他种族”,因此我们将曲线的起止点限制在1968年和2017年。
[3] Emile Durkheim, 1897, 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 , Germer Baillière.
[4] George Simpson, introduction to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 by Emile Durkheim, trans.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ed. George Simpson, Free Press, 1951, loc. 367 of 7289, Kindle.
[5]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
[6] Wilson, 254.
[7] Raghuram Rajan, 2019, The third pillar: 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 Penguin.
[8] William N. Evans, Craig Garthwaite, and Timothy J. Moore, 2018, “Guns and violenc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crack cocaine markets on young black males,” NBER Working Paper 24819, July.
[9]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1965,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0] Charles Murray,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 Basic Books; Charles Murray, 2012,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 ca, 1960–2010 ,Crown.
[11] Wilson, Truly disadvantaged , 14.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曾写下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相当怀疑这句话是否真实,但它确实适用于死亡和疾病——人不是还活着,就是已经死去,但如果他们生病,则有千万种形式。各种各样的疾病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能力。用经济学家兼哲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它降低了人类的能力。 [1] 我们在本章中探讨了几种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指标都表明,人到中年后,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差,正如死亡人数开始增加一样。中年人不仅死亡率更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在绝望的死亡中,疾病无疑是绝望的一部分。
当然,疾病和死亡并非不可分割。尽管面临死亡风险的人(例如,酗酒者或癌症患者)在死前确实健康状况不佳,但人口的健康问题(有时被称为非致命健康问题)与死亡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死去的都是最虚弱的人,那么更高的死亡率甚至可以提高活下来的人口的平均健康水平。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但活下来的许多人会身患慢性却非致命的疾病。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对于艾滋病的治疗就是一个例子。
本章着眼于活着的人的健康状况。这些数字并不漂亮,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那些活下来的人的健康指标也越来越差。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或非常好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疼痛、严重的精神抑郁,或者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人们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很难正常工作。无法工作会减少收入,从而导致其他方面的损失和困难,更不用说工作本身就是许多人满足感和意义的源泉。不能花时间和朋友相聚,不能出去吃饭,不能去看球赛,甚至连出门逛逛都不能,这些都让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正如死亡一样,健康状况恶化似乎也专门找上了那些处于工作阶段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 [2] 从这一广义角度来看,有许多指标值得关注,既有积极的方面,如身心强健的指标,也有消极的方面,如疾病的指标。与死亡率(衡量死亡的指标)相对,对于“活着但健康状况欠佳”的衡量指标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发病率”。健康状况欠佳有很多种状态,每种状态都有各自的指标。有些是在年度体检时进行测量的。血液和尿液样本可以测出胆固醇、糖尿病、心脏功能、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的指标。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员也会测量四大“生命体征”——血压、脉搏、体温和呼吸频率。近年来,医生询问疼痛状况(有时被称为第五生命体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讨论这个话题。
还有一些健康指标,即便在没有专业人士帮助的情况下,人们也能轻易知道:是否超重;是否吸烟和饮酒,以及吸烟和饮酒的量;身体和情绪上的总体感觉;能控制哪些行为,不能控制哪些行为,包括能否工作;是偶尔还是持续感到疼痛,如果是,疼痛情况有多严重。一个优秀的医生还会询问你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你的社交和情感生活。失去工作、朋友或配偶会带来强烈的情感痛苦。优秀的医生知道,人们即便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也经常会感到疼痛。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疼痛源自臆想,而且情感和身体的疼痛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试图提出全面衡量健康状况的单一指标,如指出某人的健康率是73%,没有太大意义。与生死这一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区别不同,健康和发病率有太多的维度,因而无法确定毫无争议的单一指标。有些指标不可避免地比其他指标更“软”,例如,与血压或脉搏这样的生命体征相比,对总体健康状况或生活状况的感受显然是更软性的指标。对健康状况的评估往往只能依赖自述,而对生活状况或疼痛状况的评估往往基于人们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医学专业人士的评估。没有专家能诊断你的生活如何,或者你是否饱受疼痛折磨。忽视人们的感受是一个错误,可惜医学界(和经济学界)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犯这种错误。
如果有人死亡,这个死亡案例以及所有细节都必须记录在官方的死亡证明上。正是从这些死亡证明中,我们得到了在前几章讨论的有关的死亡率信息。在全球各个富裕国家,此类死亡统计记录是标准化的。但是,如果你去医院体检或者看病,其结果并不会被记录并汇总。例如,我们并没有关于肥胖、高血压或高血脂的全国记录。如果通过医疗保险体系接受治疗,病人的医疗记录会被集中存储,但这些记录缺少关于患者个人的信息,因此,尽管记录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病情、治疗和费用的信息,但对被治疗者个人信息的记录却非常有限。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会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所有的就诊信息都会被记录,而且这些数据至少在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个人数据联系起来,例如,他们的教育、婚姻、收入和纳税状况等方面的信息。
在美国,我们依赖对家庭或个人进行的抽样调查。这些调查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但有些私人机构也会开展调查,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 [3] (BRFSS),这是一项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协调下,由各州进行的电话调查,要求人们报告与健康有关的信息。BRFSS被戏谑地称为“burr-fuss”(噗—瞎操心),每年调研大约40万成年人的相关信息,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报告疼痛等情况,并报告影响健康的行为,即风险因素,如吸烟、饮酒、身高和体重以及运动情况。
我们还参考了NHIS的数据, [4] 该调查每年访问约3.5万个家庭,深入访谈家庭中的一名成年人,并收集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该调查还询问人们与医疗系统的接触情况,例如,是否有医疗专业人员告知他们患有癌症、高血压或心脏病。这些报告非常有用,但它们的数字不仅取决于疾病的流行程度,还取决于人们接受诊疗的程度以及诊所在进行诊断时的积极性。例如,近年来甲状腺癌的诊断率有了很大提升,但该病的死亡率却没有变化,这表明实际发病率的增长远远低于检出率的增长幅度。许多诊断测试对服务提供者而言利润丰厚,因而肯定存在过度测试(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治疗)的情况。如果不同地区的过度测试情况不尽相同,那么区域或国家模式将被扭曲。
因为BRFSS和NHIS开展的是全国性调查,并且每年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们多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并寻找健康和健康性行为逐渐改善或逐渐恶化的迹象。BRFSS或NHIS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成本很高,而且依赖受访者对自己健康情况的自我报告,而不是体检和实验室测试结果,后者通常会被规模较小的调查采用,并在专门设计的移动中心进行。 [5] 例如,这些小型调查会采集血样,并由专业医疗人员测量被调查者的身高、体重和血压,而不是依赖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许多人会误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人在50岁以后会变矮,但他们会记住并报告自己年轻时的身高,完全沉浸于往昔美好的日子,男性尤其如此。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往往会低估自己的体重。 [6] 我们很难因为人们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一点而批评他们,尽管出于科学目的,了解真相是件好事。专业医学人士经常调低老年男性报告的身高数值,当他们的报告十分准确时,医生会十分惊讶。包含体检的调查不仅可以收集人们无法自行了解的健康信息,而且可以对来自规模更大、成本更低、侵入性更小的访谈性调查的信息加以交叉验证。
有关健康状况最简单的问题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按照5档打分,即优秀、很好、良好、一般或较差。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被认为不严谨。也许不同的人在说“优秀”或“很好”时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也许有些人天生坚强,在会压垮其他人的情况下仍然感觉良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还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对健康期望的影响,例如,在贫困国家中,最穷的那部分人常常比富人更多地表示自己非常健康,因为他们不能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太差,那会让他们丢了工作。 [7] 我的健康状况“良好”吗?相对于什么而言呢?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与其他指标一致,包括客观可验证的指标,而且,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它们收集的健康相关信息超过了医生从全面体检中收集的信息。 [8] 这些报告包含真实的信息,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对此加以核实,但在无法核实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图6-1显示了从BRFSS中摘录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报告其健康状况为“一般”或“较差”(我们将这两类统称为“不良”健康状况)的比例。每条线都记录了特定年份中25~75岁的人口的自我报告数据。鉴于受教育程度对于绝望的死亡率的重要影响,我们仍然按照人们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分别计算,左图和右图显示了两个群体,即只拥有低于学士学位的群体和拥有学士学位及更高学位的群体,在1993年、2007年和2017年对其健康状况的自我报告。两图的纵轴均为表示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受访者占受访者总人数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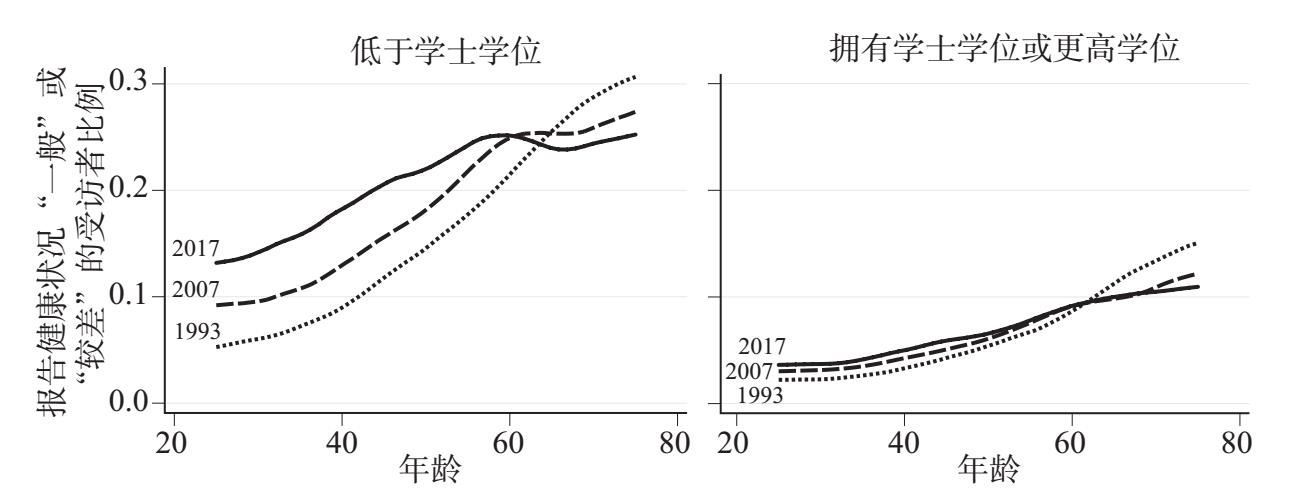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BRFSS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两个群体来说,不良健康状况的报告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有可能面临疼痛和慢性疾病等妨碍健康的状况。事实上,如果不良健康状况的报告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我们会拒绝将自我报告作为一种有用的健康衡量指标。即便如此,这种增长的趋势也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与其他同龄人进行比较,以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是那样,这些线条将是平缓的,因为平均而言,人们与同龄人的健康状况十分类似。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报告不良健康状况的比例明显不同。例如,1993年,在40岁的受访者中,没有学士学位者与拥有学士学位者(分别占总数的8%和3%)相比,前者报告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比后者高了近3倍。不过,图6-1揭示的最惊人的一点是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曲线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情况(我们也有其他年份的研究结果,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并没有将这些结果纳入图6-1)。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学士学位人口中较年轻的那批人——左图中从25岁到50岁或55岁左右的人——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这一群体在40岁时报告健康状况不佳的百分比在1993—2017年翻了一番(从8%增至16%)。在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报告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数也略有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相比不值一提,这一点与绝望的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在同一时期,60岁或以上的老年白人则报告了更好的健康状况,其中报告健康状况是“一般”或“较差”的人越来越少。到2017年,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60岁以上的成年人报告健康状况较好的比例甚至高于50多岁的人口。之所以出现这个令人费解的结果,是因为图6-1中的数字包含不同的出生队列。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中,晚出生的队列在各个年龄段都报告了比之前出生队列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因而导致这一异常结果。
鉴于在不同年份的调查中,报告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的比例增加只发生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因而驳斥了一个说法,即造成变化的原因单纯是不同出生队列的人评估健康状况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较晚出生的队列对病痛或慢性疾病更为敏感,因而导致他们报告的健康状况更差。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可以在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也看到同样的变化。而且同样并非偶然的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不同年龄的健康状况变化与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死亡率变化模式相吻合,即老年群体的情况有所改善,而中年群体的情况日趋恶化。同样,正如绝望的死亡率一样,健康状况不佳的报告率至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上涨,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继续缓慢增长。显然,死亡率的变化模式同样适用于发病率的变化。换言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年白人正在走向死亡;另一方面,那些幸存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差了。 [9]
如图6-1所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报告健康状况不佳的数量逐渐增加,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他健康指标的佐证。虽然不同统计图的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年白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白人,正身陷困境。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体现在许多方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心理健康,我们在此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进行衡量。自1997年以来,NHIS的受访者均会被问到6个问题,描述他们在过去一个月的感受,统计人员会根据他们经历每种感受的频率综合打分。当得分超过一个临界值时,受访者将被归类为经历严重的精神痛苦。这些问题涵盖受访者感到悲伤、紧张、不安、无望、一文不值,以及“难以做任何事”的频率,所有这些感受都可能导致绝望。图6-2显示了1997—2017年,25~75岁的受访者感到精神痛苦的比例。同样,左图和右图显示了没有学士学位和拥有学士学位的受访者的情况。纵轴为根据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被归为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受访者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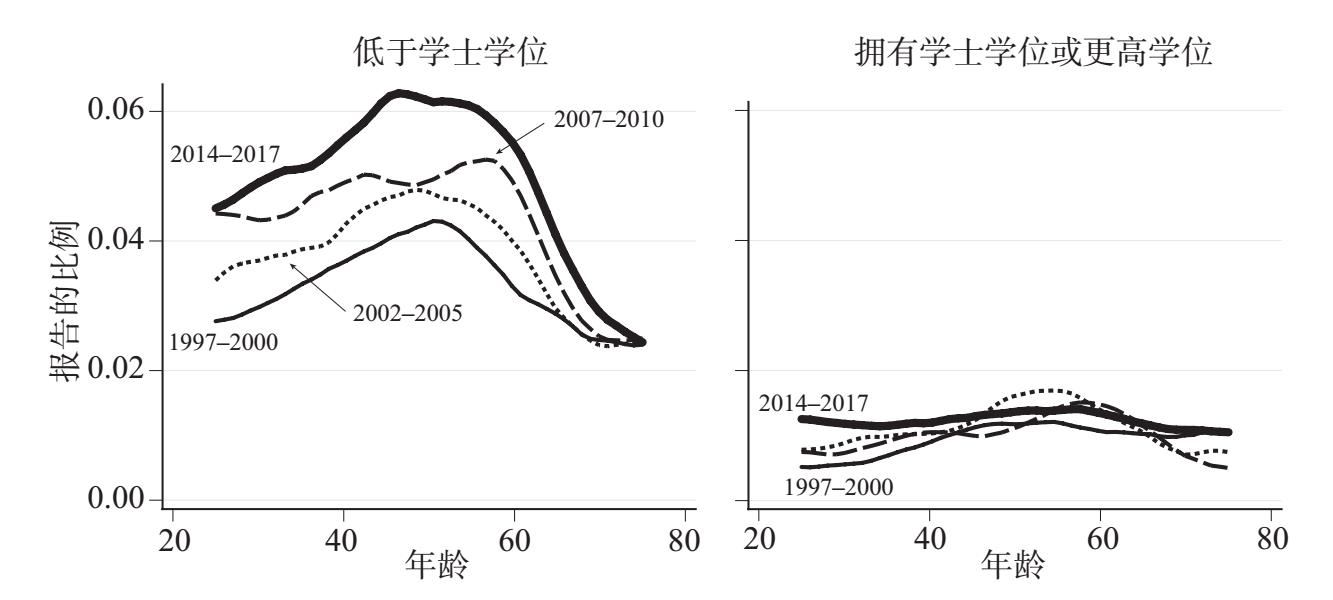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NHIS
对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中年阶段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风险最高,且在40~60岁达到顶峰。在这个年龄段,工作、抚养孩子和照顾年迈父母的压力无疑十分巨大。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精神痛苦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并不常见,尽管在过去20年中,经受精神痛苦的年轻人口的比例和中年人口一样也出现增长。同样,这种不断上升的趋势缓慢而稳定,并且上升的速度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并未加快。在50岁左右且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比例从1997—2000年的4%上升到2014—2017年的6%。
同样,正如绝望的死亡率一样,在图6-2的右图,我们将看到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情况非常不同。在这一群体中,中年人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风险也是所有成年人群体中最高的,但该风险仅为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25%。在拥有学士学位的年轻人中,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但与没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相比,增加的幅度微不足道。
还有其他指标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证明,正在经受疼痛的情况也呈现同样的状态,而疼痛在本书中扮演着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中年白人也会在完成日常活动方面遭遇困难。对这一点,健康调查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上面临困难”这一问题进行衡量的。自1997年以来,NHIS的调查一直包括相关问题,询问受访的成年人完成下列活动的困难程度,包括步行0.25英里(约三个街区)、爬10级台阶、站或坐两个小时、出门购物或看电影、在家放松,以及和朋友交往。在没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年龄白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所有上述活动中都遇到不止一个困难,而这种情况在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和老年人(65~74岁)中均没有出现。近20年来,25~54岁、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人口,对外出购物或看电影,还有在家放松方面感到困难的比例增加了50%,而对与朋友交往方面感到困难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无法与朋友交往不仅会剥夺个人享受生活中的乐趣,还会使人面临更大的自杀危险。
肥胖率的上升可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过高的体重会使人们更难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特别是当人们不再年轻时。肥胖通常通过体重指数(BMI)衡量。BMI是用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得出的数字。如果你的BMI在30以上,你就属于肥胖群体。如果你的BMI低于18.5,你就是体重过轻。然而,美国肥胖人口的增加并不能印证这些健康指标的恶化。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所有BMI水平的人口中都看到了类似的健康恶化,无论是体重过轻、体重正常,还是体重超标或肥胖人口。中年美国人并不仅仅是因为越来越胖而更不健康。
一个没有恶化的指标是吸烟人口的比例。在25~64岁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吸烟率持续下降,尽管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吸烟率仍然相对更高。1993—2017年,吸烟率不断上升的唯一群体是45~54岁且没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并且这个队列中吸烟率的增长幅度也很小,只有两三个百分点。我们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即总体而言,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吸烟率正在下降,但药物、酒精和自杀的死亡率却在上升。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以前也吸烟,感觉香烟对人的抚慰作用和酒精差不多,但没有烟酒结合的作用明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吸烟率比其他许多富裕国家低得多。
疾病会让生活变得一团糟,而且它还会干扰其他活动,无论是有直接价值的活动,如与朋友交往,还是不仅有价值,而且十分重要的活动,如工作。请注意,报告不能够工作与报告失业不是一回事,失业率会随经济状况变化而起伏不定。相比之下,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工作年龄段的白人报告无能力工作的比例就已经开始不断上升。正如图6-1和图6-2所展示的对于身心健康状况的自我报告,这个数字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也存在巨大差异。在45~54岁的人口中(传统上收入最高的年龄段),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报告不能工作的比例从1993年的4%上升到2017年的13%,而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的报告比例则自始至终都很低,只有1%~2%。
一些不能工作的人有资格享受州社会保障残疾保险(SSDI)福利。这一资格取决于该人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残疾的性质,以及该人是否有能力从事不受其残疾影响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在此讨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担心,残疾保障制度可能会诱使人们报告他们无能力工作,从而逃避工作,并寄生于其他人的劳动。 [10] 本章中某些指标的真实性无疑可能被这种扭曲的事实破坏。如果一个人实际上没有残疾,但设法申领了残疾保险金,那么当调查员询问他时,他肯定会明智地回答,他领取残疾保险金是因为没能力工作。
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报告到底有没有因残疾保障体系的存在而扭曲,但是我们怀疑扭曲的程度并不大 [11] 。正如我们在本章看到的,健康状况指标的恶化在诸多指标上太过一致,同时我们在第七章中还会再次看到,与疼痛相关的指标也是如此。此外,在那些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残疾保险福利的人口中,即那些没有足够工作年限申请保险的人口中,报告无能力工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激增与死亡大流行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也许人们假装生病是为了申领福利金,但他们正在走向死亡的事实无疑证明了真实的悲剧正在发生。
我们已经讲述一个疾病与死亡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一定有什么因素,使生活变得更糟,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来说,更是如此。人们让生活有价值的一些关键能力正在被破坏,包括工作能力和与他人一起享受生活的能力。人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断加剧。当然,经历这种生活质量恶化的人远远多于死亡的人——这种恶化无疑是死亡的大背景。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讨论另一种疾病造成的疼痛,有证据显示它与社会分裂与绝望的死亡密不可分。
[1] Amartya K. Sen,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 Elsevier.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Constitution,” accessed October 15, 2019,https://www .who.int/about/who-we-are/constitution.
[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9, “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 last reviewed August27, https:// www.cdc.gov/brfss/index.html.
[4]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19,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last reviewed August22, https:// www.cdc.gov/nchs/nhis/index.htm.
[5] BRFSS(电话调查)的样本量比NHIS(上门进行家庭访谈)多了一个数量级,而NHIS的样本量又比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多了一个数量级。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每年通过访谈、体检和实验室检测对5000人进行调查并搜集数据。美国有关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的信息,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19,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last reviewed September 17, https://www .cdc.gov/nchs/nhanes/index.htm。
[6] Majid Ezzati, Hilarie Martin, Suzanne Skjold, Stephen Vander Hoorn, an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2006, “Trends in national and state level obesity in the USA after correction for self- report bias: Analy sis of health survey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 99, 250–57, https://doi.org/10.1177/014107680609900517; Duncan Thomas and Elizabeth Frankenberg, 2002, “The measure 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health in social surveys,” in Summary measures of population health: Concepts, ethics, mea sure ment and applications , World Health Organ ization, 387–420.
[7] Amartya K. Sen, 2002, “Health: Perception versus observation: Self reported morbidity has severe limitations and can be extremely mislead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324, 860–61.
[8] Ellen L. Idler and Yael Benyamini, 1997, “Self- rated health and mortality: A review of twenty- seven community studi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 ior ,38(1), 21–37.
[9] 为了交叉检查结果不受BRFSS的某些特殊性影响,我们使用了另一项大型全国性调查NHIS来复制图6—1中的结果,并得到一致的结果。
[10] Nicholas Eberstadt, 2016, Men without work: Ameri ca’s invisible crisis ,Templeton.
[11] Jeffrey B. Liebman, 2015,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 in disability insurance benefit receip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9(2), 123–50.
适逢此世,天国降临。
欢如夏花,惊鸿一现。
幸福苦短,去日无多。
唯余苦痛,肆虐纠缠。
——玛雅·安杰卢
在我们的叙事中,疼痛(或痛苦)占据着特殊的一席之地。社会和社区困境、劳动力市场、政治和企业利益等方面都围绕它发生碰撞,同时它也是一个渠道,所有因素都通过它影响绝望的死亡。
在我们寻找死亡背后的故事时,疼痛在迥异的背景下不断出现。疼痛是导致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杀的人相信,他们无法承受之痛永远不会出现转机。对疼痛的治疗是阿片类药物流行的根源。大脑中天然的阿片肽系统控制着快感和疼痛的缓解。人们用“疼痛”和“伤害”等词描述遭受的“社会痛苦”,包括拒绝、排斥或丧失带来的痛苦。有证据表明,社会痛苦会启动一些神经过程,这些过程同样可以让身体发出疼痛的信号,就像脚趾踢到硬物或者手指被划破或者关节疼痛给人的感觉一样。止痛药泰诺既可以缓解身体疼痛,也可以缓解社会痛苦。今天,有更多美国人报告他们正在遭受疼痛之苦,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 [1]
上述关联与我们认同的说法一致,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之所以更多地感受到疼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缓慢解体。与此同时,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成为生活解体与自杀以及药物和酒精成瘾现象之间的联系。无疑,绝望的死亡之旅常常伴随着疼痛。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处于疼痛之中,这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人中表显得最明显。阿尔贝特·施韦泽曾经写道,疼痛(或痛苦)“是人类最可怕的主宰,甚至比死亡本身还可怕”。千千万万美国人的生活因疼痛而受限:有些人不能工作,有些人不能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与朋友或所爱的人共度时光,有些人不能睡觉,有些人不能进行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活动。疼痛会破坏食欲,诱发疲劳,并抑制愈合。在极端情况下,它还会侵蚀人活着的欲望。
衰老,即使正常的衰老,也会伴随着更多的疼痛。关节炎是造成疼痛最常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今天的美国,中年疼痛现象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正面临一个不同寻常的局面,即中年人中报告他们正在经历疼痛的比例事实上已经超过老年人群体。人们正在遭受多种原因导致的疼痛,或者遭受原因不明的疼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统计,超过一亿美国人患有慢性疼痛,即按照定义至少持续了三个月的疼痛。 [2] 这种慢性疼痛中的一大部分似乎不是由于某种损伤或者可以通过治疗消除的病症。许多专业医疗人员现在已经把慢性疼痛本身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虽然它仍然是一种人们所知甚少,并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曾认为疼痛是大脑应对机体损伤的一个信号,但这种认识现在已经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识,即大脑参与了所有疼痛的发生过程,同时社会性痛苦或共情性压力也能像生理损伤一样导致疼痛。 [3] 有关疼痛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定义是,疼痛就是“经历者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说它存在它就存在” [4] 。病人,而非医生或科学家,是唯一的权威。
疼痛的普遍程度因职业而异,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比坐在办公桌或电脑屏幕前工作的人更容易受伤或经历疼痛。他们随着年纪增大也更容易出现疼痛的症状,身体损耗得更快。 [5] 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疼痛更为常见,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比例更高。事实上,“劳动”这个词经常是“痛苦”的同义词,例如在《圣经·创世记》中,因为偷吃禁果,夏娃和所有女性必须经受分娩之痛,亚当及后世人类也被惩罚以辛苦劳作为生。“疼痛”(或痛苦)(pain)和“惩罚”(penalty)源自同一个拉丁词根。
疼痛(或痛苦)和工作互为因果关系。正遭受疼痛折磨的人可能因为无法工作而提出残疾保险申请,有些人会怀疑这些申请是否合理,因为人们对疼痛的真实性各执一词,所以此类申请长期以来在法律、政治和学术上都存在很大争议。人们有测量体温或血压的仪器,但没有任何仪器能够测量疼痛的等级,并且自带刻度,表明疼痛已经让人丧失能力。我们可以设想发明一种“疼痛测量仪”,带有可植入人体的传感器,并且在人的前额挂一个刻度盘,就可以对疼痛情况做出准确评估,这样肯定会大有帮助。事实上,疼痛的定义,即“经历者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给残疾福利政策带来了明显的麻烦。
疼痛症状治疗行业的公司,例如,生产止痛药的制药公司,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并不总是符合那些正在经受疼痛折磨的人的最大利益。制药公司通过销售止痛药物已经赚了数十亿美元,然而随着止痛药处方数量的上升,疼痛症的报告反而有所增加。它们只想推销自己的产品,并游说政府,以尽可能地让它们的推销更加容易。企业的行为,以及应如何监管这些行为,以使其符合公众利益,这些也是有关疼痛的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盖洛普公司定期收集美国人的大量数据。它会问受访者在前一天是否经历了长时间的身体疼痛。我们将美国划分为一个个小区块来研究疼痛状况的分布,一个区块代表人口数量足够多的一个县,或者代表相邻几个人口较少的县的集合。美国有超过3000个县,其中一些主要是山地和森林,因此通过合并,我们得出大约1000个小区块,每个区块至少有10万人口。图7-1显示了2008—2017年美国25~6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的平均疼痛状况分布,区块的颜色越深,表明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越高。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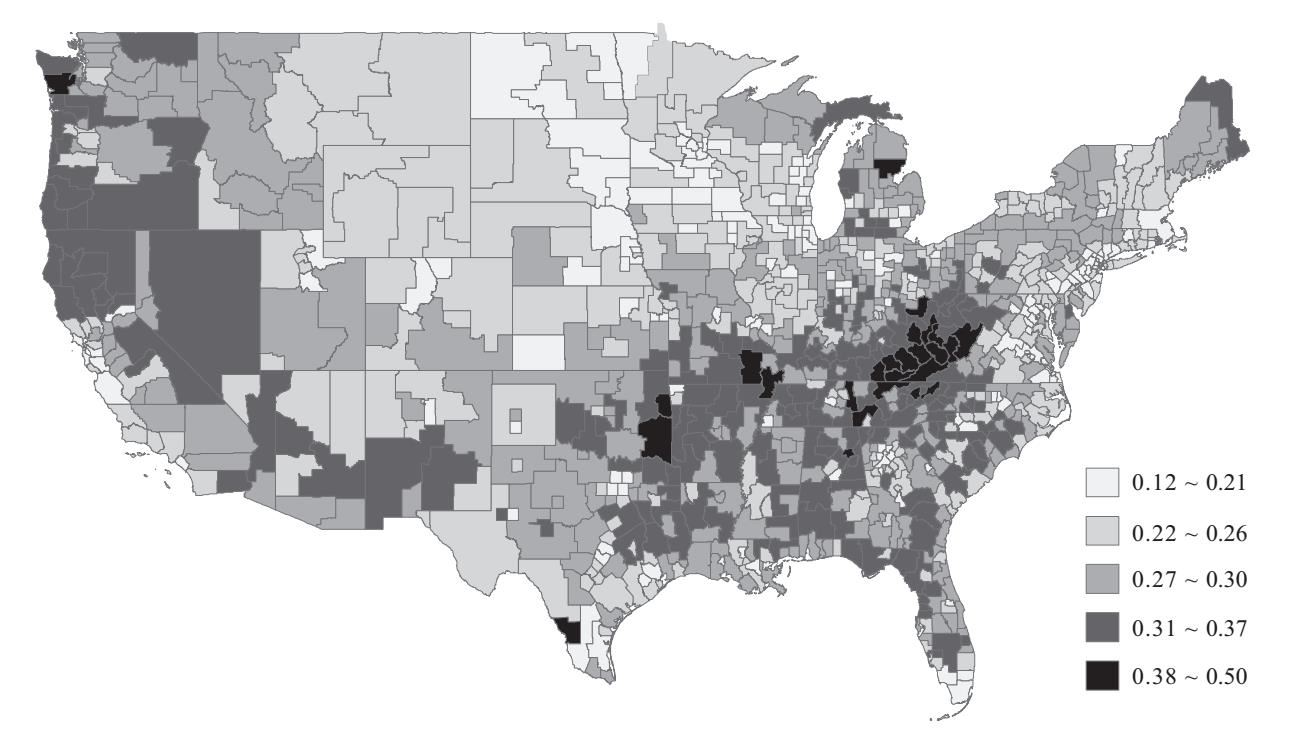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盖洛普追踪民调
在1000个小区块中,报告前一天经历疼痛的人口比例(来自盖洛普的数据)与自杀率以及更广泛的绝望的死亡率存在极大的相关性。图7-1中揭示的一个关键信息是疼痛症状在美国范围内的分布。可以看出,西部、阿巴拉契亚地区、南部、缅因州和密歇根州北部的情况很糟糕,而在中北部平原地区以及东北部的95号州际公路/美国国铁走廊和加州的湾区,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要低得多。又一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更低。在失业率更高、贫困程度更高的地区,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更高。 [7]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在不同地区中获得的选票数量也与报告疼痛的人口比例密切相关。
图7-2使用同样的数据绘制了2008—2017年,接受调查的180万名25~80岁白人人口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实线表示所有白人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它从人们在25岁时的17%上升到60岁时的30%,然后在80岁时下降到27%。请注意,图7-2并不是跟踪同一人群并描绘他们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图右侧的人口(六七十岁)和左侧的人口(二三十岁)是不同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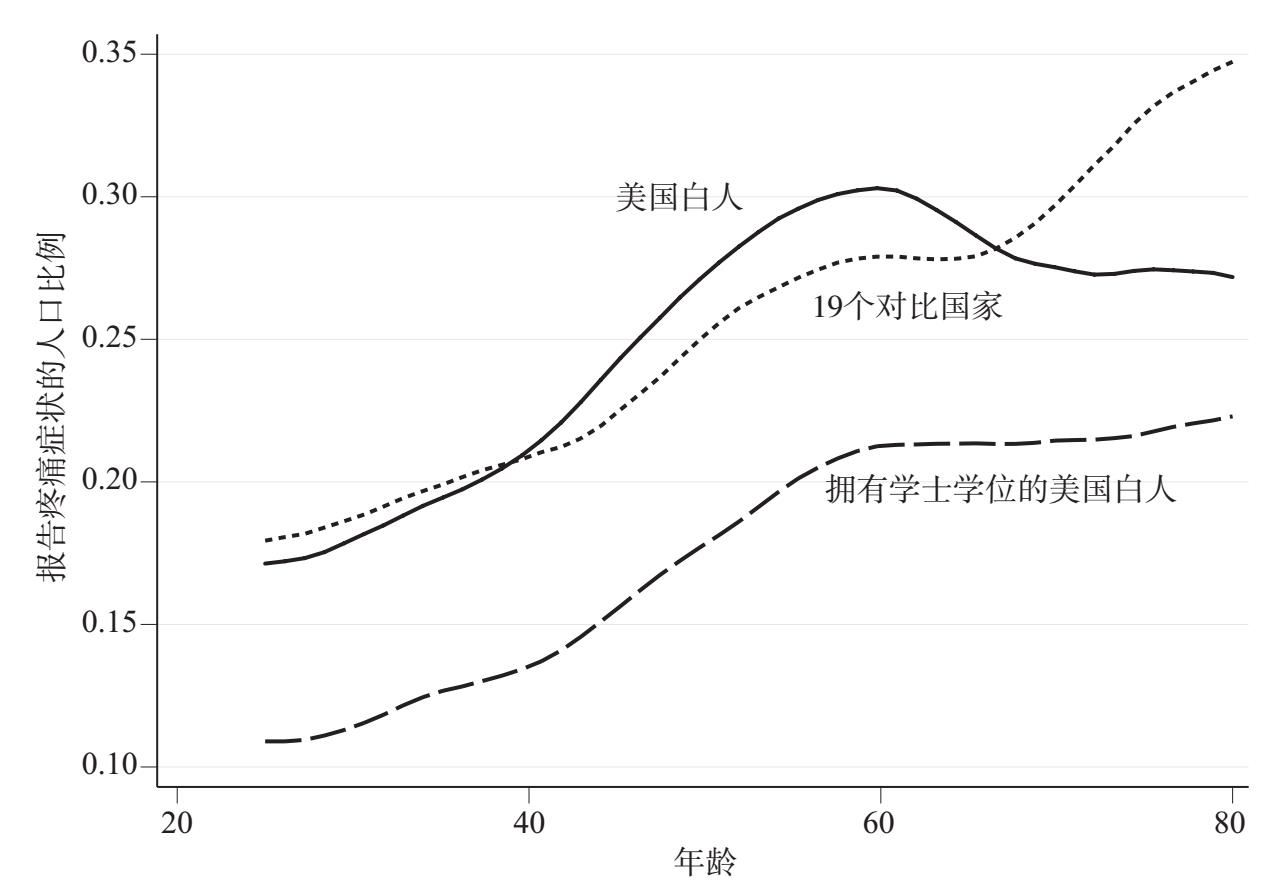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盖洛普追踪民调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这条曲线揭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年龄增长通常会使疼痛现象增加,尽管有些人会设法永远保持年轻的体魄,但人口的平均疼痛程度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来说,疼痛随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速度往往更快。想想那些包裹运送工人,他们的背部最终一定会因长年的搬运工作而疼痛,还有那些经常面临受伤风险的采矿工人或农民。当这样的人退休后,疼痛可能会暂时缓解和减轻,但随后,身体衰老必然会令疼痛再次出现。因此,我们预计,疼痛曲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60岁左右趋于平缓,然后再次上升。但图7-2中的实线并不符合这种预期,相反,60多岁的人口实际上比80岁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疼痛症状。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即疼痛症状最严重的人会更早死亡,因此幸存者的疼痛现象会减少,但死亡率从未高到足以抵消活着的人随着年龄增长而正常出现的疼痛加剧现象。
盖洛普在全球许多国家针对疼痛进行了同样的调查。 [8] 其他国家的样本数量并没有美国那么大,但如果将各国数据汇集在一起,我们可以为每个年龄组绘制一幅可信的对比图。图7-2中的虚线是其他19个发达工业化国家调查结果的汇总。 [9] 综合起来,我们在2006—2017年共有243000个调查数据。在对比国家组,曲线的起点,即年轻人的部分,与美国的情况大致相同,但曲线在40~65岁开始分化。对比国家组报告疼痛症状的年龄分布更接近我们的预期,即疼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正常退休年龄附近趋于平稳,之后又恢复上升趋势。美国白人身上出现的状况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正如美国中年死亡率的上升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一样。
最后一条线索来自图7-2中最下面用长虚线表示的曲线反映了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白人的疼痛状况,而最上面的实线反映的是所有教育水平白人的汇总情况。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经历的疼痛状况明显更少,他们中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比总人口中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少了约1/3。同时他们也符合我们预期的模式,即疼痛现象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然后在退休前后放缓,随后再度上升,尽管后来的增速较慢。显然,即便拥有学士学位,也不能预防关节炎。
我们发现,美国和其他国家按年龄段呈现的疼痛模式差异可以由下面的因素加以解释,那就是近年来,没有本科学士学位的美国中年白人报告的疼痛症状出现急剧增长。图7-2中的老年人口没有出现中年人口的疼痛症状暴增现象,如果我们跟踪他们的一生,他们也不可能会在中年时进入疼痛高峰。同样,虽然我们在获得未来的数据之前无法确定,但我们怀疑,如果我们跟踪今天中年龄段的成年人到他们的老年,他们到时候所报告的疼痛症状也将远远多于今天的老年人,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感沮丧的预测。如今的中年人正遭受非同寻常的疼痛,但与他们年老时将会经受的疼痛相比,今天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我们长期跟踪同一个人的疼痛程度变化趋势,或者至少跟踪同一年出生的人的疼痛程度变化趋势,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所做的那样,再次使用出生队列对人口进行划分,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盖洛普的数据覆盖的年限不够长,无法支持我们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转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会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三个月里是否经历持续一天以上的颈部或背部疼痛,或者慢性关节疼痛。如果只是使用这些数据简单地绘制疼痛与年龄的关系图,我们将会得到一个类似于图7-2中使用盖洛普数据所得到的模式。现在,我们还可以跟踪连续出生队列的长期状况,并按照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针对绝望的死亡进行分析时所做的那样。
图7-3显示了1930—1939年出生到1980—1989年出生,以10年为间隔的出生队列的情况。左图和右图都显示,如果我们跟踪同一组人随着年龄增长的疼痛症状变化,会发现疼痛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
在图7-3中,没有一个出生队列在60岁时出现疼痛症状逆转的迹象,尽管如果我们以某一年为节点观察图中各个出生队列的情况,将会看到图7-2所示的逆转。对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疼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那些晚出生的人在一生中将有更多的时间处于疼痛之中。对于1930—1939年出生的人,即左图最右侧曲线所代表的群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经历更多的疼痛,这是在他们60岁以上的时候观察到的。在它旁边的曲线代表了1940—1949年出生的人,他们的疼痛报告率的增长模式大致相同,但在各个年龄报告疼痛的人口比例都比前一队列高。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来说,每一个后续出生队列都会比前一辈人经历更多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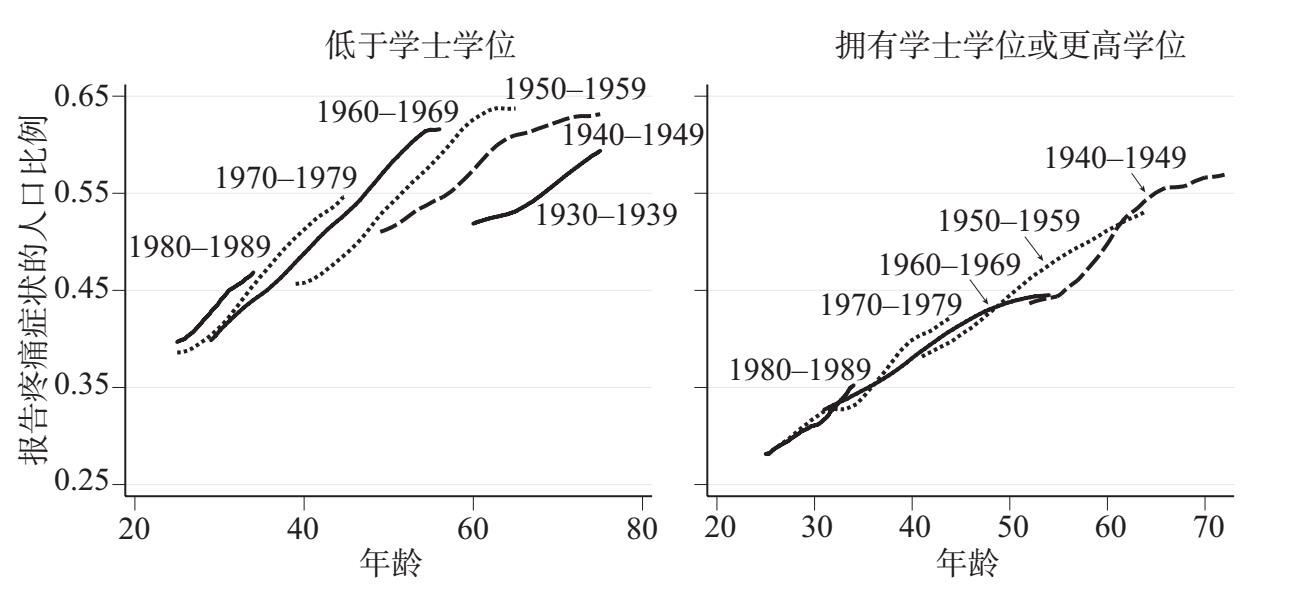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调查
而在右图中,即那些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虽然后一个出生队列与前一个出生队列相比,报告疼痛的人口比例偶尔会上升,但在任何给定年龄,各个出生队列报告疼痛的人口比例有很多重叠。换言之,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人口的曲线显示了疼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加剧的现象。无论是什么导致了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不同出生队列在疼痛方面出现差异,它们都并未影响拥有学位的人口。这意味着,所有那些中年疼痛的高峰,以及图7-2中在老龄时出现的下降,都来自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 [10]
对于疼痛加剧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所谓的“雪花” [11] 效应,即人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坚强。过去,人们往往会嘲笑那些在做牙科治疗时要使用麻醉药普鲁卡因的人,父母也不会对孩子的疼痛太在意,疼痛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能排除雪花效应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只有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成为“雪花一代”,这一点难以令人信服。
图7-3中的队列曲线与图4-3中有关绝望的死亡的队列曲线非常相似。绝望的死亡和疼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每个晚出生队列报告的疼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比之前的队列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
在过去25年里,黑人报告背部、颈部和关节疼痛的比例比中年白人的报告比例低了20%,并且两个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都是如此。然而,在每一个连续的出生队列中,没有学士学位的黑人和白人中,都有很大一部分会出现颈部、背部和关节疼痛。黑人和白人在近年来的死亡率走势并不相同,但他们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疼痛报告率的变化模式非常相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原因来解释药物、酒精和自杀造成的死亡率差异,我们在后面还会再度讨论这个话题。如果疼痛是导致绝望的死亡的原因之一,那么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有其他一些因素正在抵消其影响。
由于疼痛有其独特性,即相对于某些行为,如工作,它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所以我们很难找出导致疼痛症状增加的根源,但我们可以对相关性和模式进行观察,并借助它们思考可能的解释。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越来越胖,而肥胖会带来疼痛。这自然很有可能,但它的相对影响较小。在21世纪10年代,处于壮年(25~64岁)的白人比20世纪90年代末的白人更胖,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平均BMI已经从“正常”范围上升到“超重”范围。 [12] 同时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则从“超重”范围进一步上升,体重处于“肥胖”范围(BMI大于30)的比例从20%增加到30%。肥胖会导致更高的疼痛水平,显然,更高的体重会对背部和关节造成损害。对比1997—2000年和2014—2017年的情况,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时期,大约25%的背部、关节和颈部疼痛报告增加量可以通过BMI的变化加以解释。这一影响当然不容忽略,但除此之外,还有75%的疼痛报告增加没有得到解释。
另一个多数人可能想到的原因是,这部分人失去了一份好工作而换得一份差工作,并且会因为这些工作而经历更多的痛苦。这从社会性痛苦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但对于身体上的疼痛则不然。许多工作都有受伤的风险,或者虽不至于受伤,但是会带来疼痛。当然,人们的疼痛(使用NHIS中定义的颈部、背部和关节疼痛)确实取决于他们从事的是何种工作。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或蓝领工作的人(例如在农场工作或者从事建筑、机器操作、运输和装卸工作)相比,高管和专业人士,以及那些在销售和行政职位上工作的人更少报告疼痛。这一规则的例外是警察和消防员,对于警察和消防员而言,要想保住工作,则一定不能疼痛缠身。我们怀疑职业运动员和军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13] 但就业格局的变化并不能解释近期疼痛报告的增加,因为这种转变恰恰是从带来更高疼痛风险的职业转移到了那些不会导致疼痛的职业。如果一个工人失去了他在通用汽车或某家钢铁厂的装配线上的工作,转而从事零售业的底薪工作,工人的收入会下降,他可能对这种变化非常不开心,但装配线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可以令他免受身体疼痛的工作,相反,它比在麦当劳或沃尔玛工作更容易导致疼痛。 [14]
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来了疼痛的增加或绝望的死亡,那么认为对体力要求较低的工作正在被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取代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还有其他机制在发挥作用。低收入往往和更多的疼痛相关联,而且这种疼痛完全有可能不是因为工作造成的,而是由于失去了作为一名工人的地位和职业价值,或者因为失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是由受工会保护的高薪工作支撑的。有实验表明,社会排斥带来的痛苦在大脑中的作用与受伤带来的痛苦相似。如果是这样,劳工阶层的缓慢消亡——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对此做出更详细的讨论——很可能是慢性疼痛加剧的原因之一。
疼痛症状增加还伴随着申请残疾保险福利的人数大量增加,特别是来自社会保障残疾保险系统的人数。申请残疾保险人数的增加可以被看作一件好事,这说明人口中疼痛症状和发病率增加的现象已经引起重视。它也可以被看作一件坏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宁愿不工作和依赖别人的劳动为生,这些人声称自己遭受疼痛和抑郁症的折磨,而这两种病都无法被客观衡量。就看你选择从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人们给后一类人起了很多不讨人喜欢的外号,比如蒙骗者、装病者和索取者(与贡献者相反)。我们相信,的确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钻福利系统的空子,但是考虑到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遭受的疼痛,并且考虑其疼痛模式与绝望的死亡模式如此高的匹配度,我们怀疑取巧装病的人数并不会太多。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阿片类止痛药的使用量大幅增加,且不论这些药物潜在的副作用,包括上瘾和死亡,单看同一时期疼痛症状的报告量大幅增加,就让这些药物的有效性面临重大挑战。不可否认,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没有阿片类药物,疼痛症状的报告数量可能更多。换言之,一些至今尚未确定的原因迅速推高了疼痛水平,超过了阿片类药物能够抑制的速度。
女性报告疼痛的比例高于男性,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因此,这一点不太可能帮助我们揭示美国特有的疼痛状况的根源。图7-3所示的情况,即按出生队列划分,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出现疼痛加剧的模式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同样,在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按照出生队列获得的年龄—疼痛模式也没有因为性别不同而发生改变。
我们还可以研究其他一些独特的现象,这些现象似乎伴随着更多的疼痛而出现。其中之一是失业,或者按照更宽泛的定义,退出劳动力市场。考虑到残疾往往是无法工作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些报告出现疼痛症状的人还报告,他们不能够购物、在家放松、与朋友交往,或者毫无困难地走过三个街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受到限制的程度更高。在报告疼痛症状的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往往还会受到更多的活动限制。此外,疼痛还和严重精神抑郁的风险高度相关,同样,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这种相关性是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两倍。
随着夏天逝去,幸福和快乐被带走,“唯余苦痛,肆虐纠缠”。
[1] Naomi I. Eisenberger, 2015, “Social pain and the brain: Controversies, questions,and where to go from her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 ogy , 66, 601–2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 -psych-010213-115146.
[2]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7, Pain management and the opioid epidemic: Balancing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benefits and risks of prescription opioid use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https://doi.org/10.17226/24781.
[3] Rob Boddice, 2017, Pa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Oxford; Antonio R. Damasio,2005,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 Penguin.
[4] Margo McCaffery, 1968, Nursing practice theories related to cognition, bodily pain and man-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tudents’Store, quoted in Ameri-can Pain Society, n.d., Pain: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s , 4.
[5]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2005, “Broken down by work and sex: How our health declines,” in David A. Wise, ed., Analyse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185–212.
[6] 此图绘制的年龄范围是25~64岁,而不是45~54岁的白人,这样做是为了可以使用更大的样本来估算小区块的人的疼痛状况。
[7]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2017, “Suicide, age, and well- be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David A. Wise, ed., Insight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307–34.
[8] Gallup World Poll,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https://www .gallup .com /analytics /232838/world-poll.aspx.
[9] 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10] 盖洛普调查中提出的问题与“昨天”有关,而NHIS中提出的问题与过去三个月有关,这可能是NHIS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更高的原因。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两种调查存在类似的规律,即60岁之前比60岁之后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增长更快。我们无法解释图7—2中欧洲老年人疼痛程度较高的现象。
[11] “雪花”指“雪花一代”(snowflake generation),这一概念出自2016年版的《柯林斯大词典》,指21世纪10年代的青壮年。他们与前几代人相比,适应性差,且更容易愤怒,看似自信满满,实则禁不起打击,就像雪花一样易融化。
[12]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年度行为危险因素监视系统调查。
[13] Case and Deaton, 2005, “Broken down.”
[14] Greg Kaplan and Sam Schulhofer- Wohl, 2018, “The changing (dis)- utility of 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2(3), 239–58.
2017年,多达15.8万名美国人死于绝望的死亡,即自杀、药物过量使用、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这相当于每天都有三架737 MAX客机发生空难,并且没有幸存者。在本章和第九章,我们将研究这些死亡发生的背景,了解这些死亡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并探讨这些信息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过去的20年中,为什么绝望的死亡数字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中迅速上升。
这三种类型的绝望的死亡都与死者的某些行为相关,最一目了然的是自杀这种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但使用药物和长期酗酒同样也是造成死亡的原因。很久以前,埃米尔·杜克海姆曾说过,要理解自杀现象(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绝望的死亡),我们应超越个体本身审视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崩溃和动荡如何导致其不能再为成员提供良好生活的环境。 [1] 杜克海姆认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自杀。然而在当前的美国流行病中,与疼痛和疾病发生的规律相一致,自杀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也许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自相矛盾的是,这又符合杜克海姆的观点,因为正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世界现在处于动荡之中。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社会和经济动荡彻底打乱了这些人的生活,并且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人们感到不再有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或者感到死亡似乎比活着还好,人们就会选择自杀。绝望的感觉可能已经笼罩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比如那些身患绝症或者长期患有抑郁症的人;这种感觉也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比如突然感到极度沮丧,或者借用英国法医的术语——“心灵的平衡被打乱”。大多数自杀都与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有关。2017年,美国有4.7万人死于自杀。
自杀是一种绝望的死亡。其实,当人们面对可能导致自杀的困境时,可能会转向不那么极端的方式,借助药物或酒精逃避痛苦、孤独和焦虑。药物和酒精可以带来某种快感,至少能够暂时缓解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会更加耐受药物和酒精这种有毒物质,因此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带来同样的快感,一些人因而上瘾。“上瘾”并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描述了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由于人们对某种物质的需求变得如此绝对,以致其他一切都被置于一边。于是人就会成为这种瘾的奴隶,宁愿以撒谎或偷窃保护和喂养它。人们常说,瘾就像一座监狱,虽然锁装在了里面,但这并没有让越狱变得容易。所谓“自私的大脑”只关心确保嗜好得到满足, [2] 它使人们无法再关心自己的行为、自己造成的危害,或者自己毁掉的生活。
用一个正在戒毒的海洛因瘾君子的话来说,上瘾“(显然)往往始于喜欢药物所带来的某些感觉(温暖、欣快、归属),或者药物消除的其他一些感觉(创伤、孤独、焦虑),通常这两者会同时发生” [3] 。温暖、欣快和归属的感觉与一个想自杀的人的感受恰好完全相反。一位权威人士曾写道:“包括人类在内,所有动物的大脑中都有快乐中枢和疼痛中枢。这些中枢由神经递质控制,后者对行为有很大影响……通过各种各样的复杂机制,所有滥用的药物都会刺激大脑的快乐中枢,并抑制大脑的疼痛中枢。” [4]
滥用药物和酗酒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杀。当快感无法形成或消退之时,或者当一个人在努力保持清醒的斗争中故态复萌,并因此而羞愧不已、自暴自弃和陷入抑郁时,与再次陷入瘾中无法自拔相比,死亡似乎成为更好的选择。许多自杀行为都既与上瘾,又与抑郁相关。心理学家兼作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曾写道:“药物和情绪障碍往往会相互影响并导致恶性循环。这两者中任何一个已经十分可怕,而二者交织在一起则能够杀人。” [5] 酒精成瘾和药物成瘾同样具有破坏性,无论是对成瘾者本身还是对他们所爱的人来说均是如此。深陷药瘾或酒瘾会令自杀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一个高度上瘾的人往往已经失去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毋庸置疑,许多人并不想死,即使身陷瘾中无法自拔,甚至即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能戒掉毒瘾,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将某个死亡案例归类为自杀非常困难,因而在统计数据中,自杀的人数几乎肯定被低估了。自杀往往伴着耻辱感,因此死者的家庭会抵制这个标签。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自杀都被视作一种犯罪,会被处以没收财产和禁止体面埋葬的惩罚。人们可能会选择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以求一死,比如鲁莽地驾驶或在危险的环境中独自游泳。在关键人物,即死者,已经不能开口的情况下,其行为的意图往往难以确定。因此,我们难以确定自杀的衡量标准,这是我们对自杀、酒精和药物相关死亡进行联合调查的一个原因,综合统计往往比单独对某一类型的死亡进行统计更准确。同时,这样做也是出于分析的需要,即将自杀、酗酒和滥用药物导致的死亡归为一组可以捕捉到它们发生的根本性原因——绝望。如果分别对某种类型的死亡进行分析,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自杀性的死亡往往发生得很快,特别是在使用枪支自杀,或者从高处坠落、自缢身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医疗救治的机会很小。使用药物和酒精自杀的结果不那么确定,这一类死亡往往耗时更久,所以尝试失败或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的可能性更大。
酒精和药物滥用从出于享乐目的的使用到耐受,再到上瘾,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酒精可能导致绝望的死亡,但也有许多人在成年后的一生中都能愉快而安全地享受美酒。大量饮酒与许多类型的死亡有关,包括自杀、药物过量使用(这种情况下酒精的存在很常见),以及因心血管疾病死亡,尤其是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后者仅在2017年就杀死了4.1万名美国人。与自杀和药物过量使用不同,酒精性肝病的死亡往往发生在中年或更晚,因为摧毁肝脏这样一个强健的器官需要时间。不过,由于年轻人中酗酒者的数量急剧增长,因此与酒精相关的死亡数量在较为年轻的人群中也开始上升。
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会被归类为“意外”死亡,除非是故意过量使用药物致死。然而,“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是有意求死,但他们在使用那些有毒物质时是明知故犯的。因此,这样做带来的致命药物过量使用或药物相互作用严格上讲并不能算真正的意外” [6] 。如果一个手臂上扎着针头的人死去,除非有其他证据表明死者有自杀的意图,否则他的死亡将被记录为意外死亡。甚至在死者曾有过多次过量使用药物并被急救人员救活的记录时,也会如此归类。对于嗑药的人来说,戒断后的复吸可能立即导致死亡。由于身体失去耐受性,再服用戒毒前可以带来快感的“安全”有效剂量可能致命。2017年,美国有70237人因药物过量使用而“意外死亡”。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死亡的共同特征,特别是社会动荡这一共同背景。这三类死亡的人数都在迅速上升,2017年,这三种类型的死亡总人数达到15.8万。相较而言,2017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4.01万,低于自杀单类死亡人数,而同一年死于谋杀的人数是19510。
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放在自杀和酒精上,尽管很多关于酒精的讨论也适用于药物。在第九章中,我们将讨论当前药物滥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将阿片类药物单列一章,部分是因为有很多内容需要讨论,同时也因为,这一药物流行病的病因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绝望的死亡发生的大背景,特别是企业界和联邦政府行为的影响,后者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题。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中,自杀和其他绝望的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15~74岁全年龄段都是如此。这导致了美国的自杀率在所有富裕国家中居于首位,而在过去,美国的自杀率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当。女性的自杀人数大大低于男性,这部分是因为她们选择的自杀手段不如男性有效(相对于男性选择的枪支,女性往往选择药物),部分是因为是她们比男性更不容易受社会孤立影响。即便如此,白人女性的自杀率与白人男性的自杀率持续同步上升。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在有可靠数据的国家,2000年以来的自杀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一些群体自杀率出现下降已经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包括亚洲(得益于更大的自主权和城市化进程),苏联国家的中年男性(得益于生活更加安定),以及几乎全世界各国的老龄人口(得益于拥有更多的资源)。美国白人的自杀率以其顽固的上升趋势成为全世界的异类。
关于自杀并没有什么简明的理论,也没有确定的方法确定谁会自杀或者为什么自杀。对于个体来说,预测自杀风险的最佳因素是其此前是否曾尝试过自杀,这个信息对护理人员很有用,但无助于解释自杀人数为什么一直在增加。不过,我们也可以找出一些潜在的影响因素,比如疼痛、孤独、抑郁、离婚或失业,因此,如果社会变化导致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普遍,或许可以成为美国总体自杀率上升的一个解释。此外,在个人行为或直接行为的背后也有社会根源。我们此前曾引用过杜克海姆的观点(其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一座里程碑),这种观点坚持认为,要想了解自杀行为,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根源,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体。正如人们经常说的(并且不完全是在开玩笑),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而社会学家则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在自杀问题上,社会学家一直做得比经济学家更好。
就自杀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理性”的自杀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自杀,是出于“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7]
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视为“今天是个求死的好日子”理论。也就是说,虽然今天就死去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比起未来要面对的苦难,今天去死就不那么糟糕了。这种理论,虽然往往遭到嘲笑(而且这种嘲笑通常是其应得的),但也不乏道理。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无法解释人们已知的关于自杀的很多信息。与此相反,杜克海姆的理论则指向社会动荡,而这正是今天美国劳工阶层在经济、家庭和社区生活等方面都正在面对的。
当求死很容易时,自杀的可能性更大。毫无疑问,决心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总会找到办法:到处都是可以跳下的高楼,上吊用的绳子也随处可以找到。但自杀是否便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想自杀的感觉往往转瞬即逝,如果能够有效地控制那些便于人们杀死自己的手段,自杀事件将有可能减少。
在英国,北海天然气得到广泛使用之前,烹饪和取暖主要使用煤气,而煤气中含有的一氧化碳可用来自杀。于是,在19世纪末煤气进入生活后,使用煤气自杀的行为大量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自杀事件是诗人兼小说家西尔维娅·普拉斯于1963年2月将头伸入煤气炉中自杀身亡(普拉斯在此前还曾两次试图用其他手段自杀,因此她的例子或许更能说明应如何预测自杀行为,而不是控制自杀手段)。1959—1971年,煤气逐渐被天然气取代。由于天然气中只含有很少或根本不含一氧化碳,自杀率在随后显著下降,尽管当时采用除煤气之外其他手段自杀的比例有所上升。 [8] 借助汽车尾气自杀的比例也曾一度上升,但随着汽车全面安装催化转化器,自杀率再次下降。因此,可以预测的是,由于一些自杀行为是由暂时性的抑郁引发的,如果自杀行为实施起来不是那么方便,这种抑郁就不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9]
美国的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虽然我们不知道枪支的供应量是否有所增加,但自2000年以来,每年被枪杀的人数和涉及枪支(包括自杀)的死亡率都有所上升。 [10] 在美国,自杀与枪支供应之间的联系既存在争议,也遭到政治化。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尽管也有一些可信的相反证据。 [11]
我们当然不应该忽视自杀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枪支供应的增加。美国步枪协会一直在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不要为该类课题研究或数据收集提供资金。
社会孤立是导致自杀的危险因素。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我们发现中年人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孤立、健康不佳、精神痛苦和疼痛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白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自杀率为什么会上升。美国人比过去更不信任他人,而信任度下降是社会资本下降和死亡风险上升的标志。 [12] 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们将讨论下列三类白人人口的同步增长,即脱离劳动力市场、没有宗教信仰以及没有结婚的白人。这些人因为脱离了具有保护作用的社会机制,因而面临更大的自杀风险。拥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与配偶和孩子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以及有一座有助于解决精神需求的教堂可去,这些都有助于维持生命的价值。这些重要的因素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白人中日渐缺席,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美国各个地区的情况来探讨社会孤立、疼痛和自杀之间的联系。美国沿着落基山脉,从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阿拉斯加,存在一条“自杀带”。全美6个自杀率最高的州是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州、怀俄明州、新墨西哥州、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它们全部位于美国每平方英里 [13] 人口密度最低的前十个州之列。美国自杀率最低的6个州是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其中5个州是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最高的十大州之一,加利福尼亚州则排名第十一。枪支在人口较少的地区很常见。犹他州是美国最健康的州之一,人口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邻近的内华达州要长两年,内华达州是美国最不健康的州之一。然而,两者都不能免于高自杀率。新泽西州默瑟县,即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和我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的地方,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632人。默瑟县的自杀率仅有蒙大拿州麦迪逊县的25%,后者美丽多山,与世隔绝,是我们每年8月都会长住一个月的夏休之所。 [14] 麦迪逊县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仅有2.1人。人口不足也意味着医疗救助人员可能离得很远并无法及时赶到,而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如果身边还有别人,人们不太可能自杀。
美国自杀率较高的州同时也是人们报告疼痛比例较高的州。 [15] 同样的模式出现在美国数千个县,那些报告在昨天长时间经历身体疼痛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也正是自杀率较高的地区。 [16] 不过,此类依赖于地域证据的结果,受制于所谓的“区群谬误”。如果疼痛是导致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我们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我们可能会预测,疼痛报告较多的地区也会是自杀人数较多的地区。然而,这样的发现并不能证明疼痛是自杀率升高的原因。落基山脉地区的居民需要修筑篱笆、驾驭牲畜或搬运灌溉管道,因而腰酸背痛或者膝盖损伤的情况多发,落基山脉的居民也可能因为人口密度低而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疼痛水平和自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但在这种情况下,疼痛高发源自农业是这些地区主要就业岗位的事实,而与这些地区因为人烟稀少和社会孤立而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无关。基于整合地理数据做出的分析永远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便如此,地理证据可以对我们从其他来源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核实。杜克海姆十分依赖地理证据,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显而易见,我们无法询问死者,所以关于死者的信息非常有限。
受教育程度和自杀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杜克海姆认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自杀,因为教育往往会弱化能够阻止自杀行为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这在过去的美国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自从1992年,几乎所有州的死亡证明上都要记录死者的受教育程度以来,受教育程度与自杀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图8-1显示了按出生队列(1945年出生的人口与25年后,即1970年出生的人口)和受教育程度(拥有或没有学士学位)划分的白人群体自杀率。第一个队列在1970年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个队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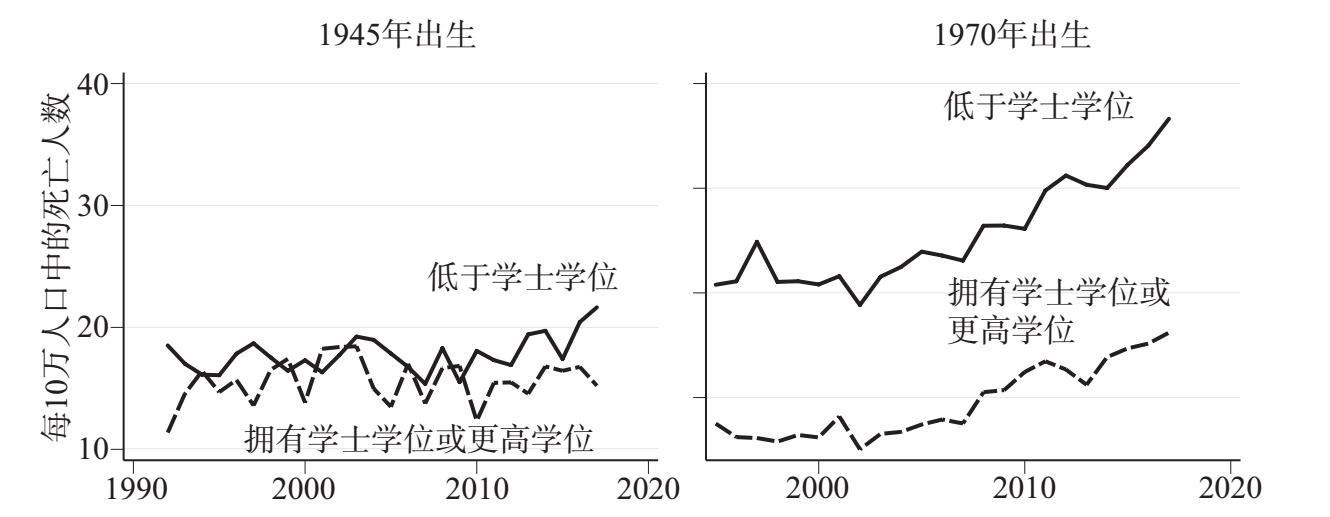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左图显示了1945年出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自杀率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的自杀率的差异不大。右图显示了1970年出生的人口,两个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自杀率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首先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中,并且在后来出生的人口中,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下一个出生队列人口的自杀率会与前一个出生队列重叠。也就是说,1950年出生的队列与1945年出生的队列遵循相同的年龄分布,1955年出生的队列则会遵循与1950年出生的队列相同的年龄分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年龄分布则随着每一个连续的出生队列而上升和变陡。 [17] 尽管图8-1描绘的是自杀而非绝望的死亡的整体情况,但它与图4-3密切相关。如果在美国,受过更多教育确实曾经令自杀的风险加大,那么现在这对白人来说已不再是事实。或者换一种更接近我们论点的说法,自杀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失业,包括对可能失业的恐惧,已经被证明会导致自杀。脱离劳动力市场也是一个风险因素。这两者都符合杜克海姆关于社会动荡和自杀的理论。的确,杜克海姆认为,“经济危机”会导致自杀,尽管他对经济危机的定义不仅包括经济衰退,还包括经济大繁荣。重要的是平衡的打破,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而不是收入水平本身,这可能正是收入水平对自杀的影响并不明确的原因。
对酒的赞美并不鲜见。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美酒令日常生活更加轻松和惬意,让人更放松和更加宽容。”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曾写道,葡萄酒“不只是单一的感官享受,更是一种愉悦与鉴赏”,尽管美酒未能阻止海明威结束自己的生命。马克·吐温则曾经说道:“什么东西过量了都是不好的,但是威士忌好酒从来没有过量的时候。”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报告(质量参差不齐),证明适量饮酒对健康有益。很多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酒精,或者至少需要借助酒精来润滑。好的葡萄酒一瓶就要几千美元,一些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也价格不菲。政府也喜欢酒类,因为它们是收入来源之一。
然而,酒精的危害也深植于历史和政策。伊斯兰教、许多福音派新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都禁止饮酒。浸信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许多印度教徒也不鼓励饮酒。大多数富裕国家对于何时何地允许销售和消费酒精都有法律规定。在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有禁酒的城镇。20世纪初,禁酒运动在许多女性的支持下(她们将酒精视为女性和家庭问题的根源),通过1920年的宪法修正案成功地在美国全面实现禁止酒精饮料,该法案最终于1933年被废除。
禁酒措施虽然经常被特殊利益集团出于私利而加以利用,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许多人难以约束自己的饮酒量,因此如果有外力的帮助效果会更好。尤利西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防自己在听到塞壬的歌声时跳进海里。饮酒过量的人可能会对他人和自己带来危险,例如酒后驾驶或操作机器,或者因酒精的影响忽视对他人的责任。在禁酒时期 [18] 之前,正如在今天,许多女性认为酒精导致男性无法养家糊口,也无法控制对妻子的暴力行为。
酒精中毒是一种酒精成瘾现象,成为酒鬼的机会因人而异,而且很可能是某种基因引起的。即使在允许饮酒的老鼠中,也只有少数老鼠不能停止饮酒。 [19] 18世纪的医生本杰明·拉什最早提出了酗酒是一种大脑疾病,而非意志薄弱。这一观点在今天被广泛接受,但我们还远不能预测到底哪些人更容易成为酒鬼,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亚伯拉罕·林肯认为,这种疾病倾向于打击“聪明而热血之人”,而“放纵的恶魔似乎总是乐于吸取天才和慷慨之士的鲜血” [20] 。林肯本人滴酒不沾,但他以典型的慷慨和洞察力充分理解了“恶魔”是如何工作的。
许多饱受酒精困扰的人依靠他人的帮助来保持清醒。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嗜酒者互诫协会拥有约6万个团体,定期在美国各地的社区聚会。在它成立之前,还曾有过一个名为“华盛顿人”的组织,林肯的上述讲话就是针对这个组织发表的。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团体支持酗酒者的家人和朋友,这再次证明了身陷酒瘾的巨大代价,这不仅对酗酒者本人,也对那些关心和在意他们的人带来巨大伤害。有关这些团体有效性的证据难以确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匿名性使得嗜酒者互诫协会无法保存记录,不过,考虑到有超过100万人定期参加聚会活动,这表明他们的确从中得到了一些东西,而且科学证据也相对积极。 [21]
甚至政府对酒精的态度也存在矛盾,有些政府对其颇为依赖,甚至可以说也已上瘾。酒精税和烟草税之所以被采纳,原因之一是它们属于“罪恶”税,这种税的征收对象是许多人并不想用,但却无法不用的东西,因此他们对税率并不敏感。反过来,国家一方面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度,强调这一税赋有助于人们克制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则赚得盆满钵满。在其早期历史上,美国政府和当今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府一样,严重依赖对商品征税,包括对酒精征税。1913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引入所得税,增加了一个税收来源,从而减少了政府对酒精的依赖,并有助于禁酒令的颁布。不可辩驳的是,允许征收所得税和颁布禁酒令的宪法修正案,连同赋予女性选举权和实行参议员直选,都是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巨大成就。
虽然适度饮酒是否对人有好处仍存在争议,但没有人会反对长期大量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长期酗酒最终会摧毁肝脏,主要表现是肝硬化,这是一种最终不可逆转的肝损害,使肝脏难以发挥其重要功能,并增加肝癌的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之一,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宣称,研究表明,酒精与肝癌以外的某些癌症,包括乳腺癌、食道癌、头颈癌和结直肠癌之间也存在关联。它还列出了其他面临风险的器官,包括心脏、大脑、胰腺等。 [22] 如果将所有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其结论都是可信的(对其中许多研究而言,其结论的可信性确实非常存疑),那么即使是极少量的酒精,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23] 当然,适度饮酒的风险非常小,不比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风险更大,况且酒精饮品还能让大多数饮用者感到快乐和放松。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的饮酒率更高,不过酗酒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更为普遍,而后者的危害尤其严重。2015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学毕业生中,80%的人偶尔饮酒,20%的人完全不饮酒。在那些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口中,这一比例更为均衡,有48%的人滴酒不沾。按照收入划分的模式与此相似,在高收入的美国人中,完全不饮酒的人口比例较低。2018年,63%的美国人饮用啤酒、葡萄酒或烈性酒,这一比例在75年的时间里变化不大。盖洛普的问卷还包括一个问题:“在你的家庭里,喝酒是否曾成为引发麻烦的原因?”
1948年,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是”的比例约为15%,到70年代初,这一比例为12%。此后明显上升,至2018年达到33%以上,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24] 这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发现,1970年是开始出现问题的关键年份,饮酒问题的上升趋势只是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病态症状之一。
图8-2显示了全体白人报告的每次饮酒时的平均饮酒量,包括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每个出生队列的人口都报告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喝的酒越来越少。但从图8-2中人们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年轻人口在任何特定年龄段都报告了更高的单次饮酒量。尽管饮酒的频率较低,但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狂饮),比每天适度饮酒对肝脏的危害更大,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患酒精性肝病的风险更高。与此相呼应的是,我们已开始看到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白人死于酒精性肝病的人数正在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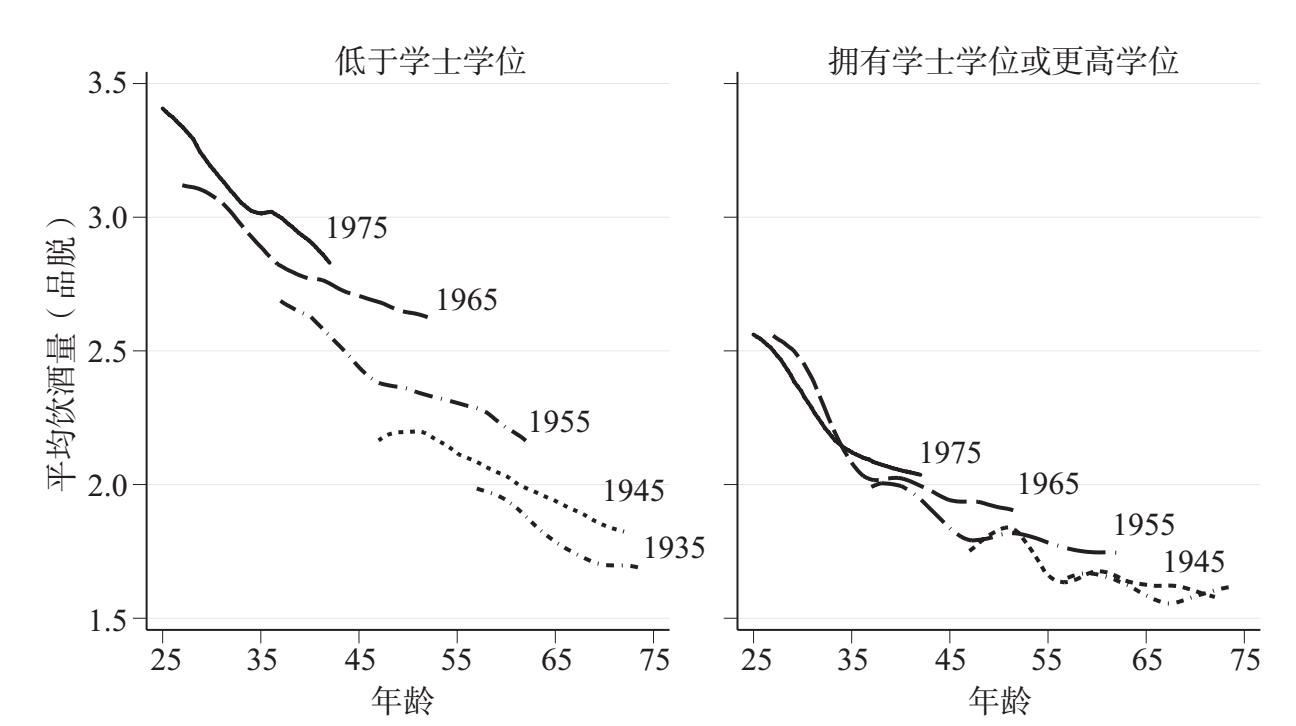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BRFSS
酒精还曾与近年来另一个死亡率飙升的现象密切相关,不过它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在俄罗斯,酒精的消费量一直非常高。20世纪80年代初,俄罗斯的人均纯酒精年消费量超过14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在20多年间,俄罗斯女性的预期寿命一直停滞不前,而男性的预期寿命则不断下降,而同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预期寿命一直在提高,特别是在1970年之后。从1984年开始,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严厉的禁酒政策,大幅减少酒精饮品的产量,提高售价,并限制消费次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由于与酒精相关(自杀、事故和心脏病)的死亡率迅速下降,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2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3岁。但是这一政策极不受欢迎,并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因此在1988年被正式废止,尽管逐渐放松管制花了一段时间。当然,这项政策后来因为更大的历史事件而被彻底淡忘,尤其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预期寿命的提升势头迅速逆转,1987—1994年,男性预期寿命下降了7.3岁,女性预期寿命下降了3.3岁。 [25] 不过此后,这个数字又有所回升,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再度接近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糟糕的)趋势为基准的合理预期水平,就好像从未有过禁酒运动,也从未经历苏联解体一样。然而,自2005年以来,俄罗斯在平均预期寿命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也许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拖延,俄罗斯终于也像40年前的北美和欧洲一样,开始有效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当美国遭受死亡流行病折磨时,俄罗斯似乎已经战胜自己的痼疾。 [26]
我们该如何看待俄罗斯发生的一切?许多评论家将俄罗斯的死亡危机与旧秩序的解体带来的社会动荡联系起来,这完美地契合了杜克海姆的理论。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但酒精在其中的角色,以及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和其随后的失败是得到广泛接受的说法,因而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死亡率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因禁酒运动而暂时推迟的死亡人数反弹,同时也因为不存在任何因素能够阻止这一反弹完全抵消最初的效果。在国家崩溃的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其他不幸事件。许多老年人失去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障。 [27] 尽管许多俄罗斯年轻人得以享受到国外旅行和受教育的新机会,但他们的祖父母除了绝望外几乎别无所得,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开始新生活。在苏联的所有国家中,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28]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发生在俄罗斯的戏剧性事件与美国过去20年的事件之间毫无关联。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俄罗斯人长期遭受难以言喻的苦难。俄罗斯的自杀率很高,匈牙利、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等许多东欧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尽管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自杀率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令人震惊和深切关注的是,在一些国家自杀率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自杀率却开始上升,从而使美国白人在这一痛苦指数中与上述国家为伍。在这些国家,自杀率与酒精导致的死亡率相关,这一点也与美国各州的情况一样。这一组国家可以被称为“耻辱之组”。这些国家根本无法保障其相当一部分人民的基本生活。将这些东欧人民长期以来遭受的痛苦与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自杀、酗酒和过量使用药物的绝望浪潮加以比较,并未夸大其词。
[1] Emile Durkheim, 1897, 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 , Germer Baillière.
[2] Robert L. DuPont, 1997, The selfish brain: Learning from addiction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Kindle.
[3] Zachary Siegel, 2018, “I’m so sick of opioid disaster porn,” Slate , September 12, https:// slate.com/technology/2018/09/opioid-crisis-photo-essays-leave-out-recovery.html.
[4] DuPont, Selfish brain , loc. 2093 of 8488, Kindle.
[5] Kay Redfield Jamison, 2000, Night falls fast: Understanding suicide , Vintage,128.
[6] Ian R. H. Rockett, Gordon S. Smith, Eric D. Caine, et al., 2014, “Confronting death from drug self- intoxication (DDSI): Prevention through a better defini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 104(12), e49–55, e50.
[7] Daniel S. Hammermesh and Neal M. Soss, 1974, “An economic theory of suici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1), 83–98; Gary S. Becker and Richard A.Posner, 2004, “Suicide: An economic approach,”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ast revised August, https://www .gwern .net /docs/psychology/2004-becker.pdf.
[8] Norman Kreitman, 1976, “The coal gas story: United Kingdom suicide rates,1960–71,” Brit ish Journal of Preventive Social Medicine , 30, 86–93.
[9] Kyla Thomas and David Gunnell, 2010, “Suicid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61–2007: A time-trends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39, 1464–75,https://doi.org/10.1093 /ije/dyq094.
[10] John Gramlich, 2018, “7 facts about guns in the U.S.,” Fact Tank,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27,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12/27/facts-aboutguns-in-united -states/.
[1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5, “Firearms and suicide,” in Firearms and violence: A criti cal review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52–200.
[12] Robert D. Putnam,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Simon and Schuster.
[13]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14] CDC Wonder, average suicide rates over the period 2008–17.
[15] 美国50个州的相关系数是0.4。
[16]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2017, “Suicide, age, and well- be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David A. Wise, ed., Insight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307–34.
[17] 1945年和1970年的出生队列中获得学士学位人口的比例并没有很大差异,因此,这些结果不太可能归因于两个出生队列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构成上发生了变化。
[18] 禁酒时期指1920—1933年。在此期间,美国推行全国性禁酒,禁止酿造、运输和销售含酒精饮料。——译者注
[19] Eric Augier, Estelle Barbier, Russell S. Dulman, et al., 2018, “A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choosing alcohol over an alternative reward,” Science , 360(6395), 1321–26, https://doi.org/10.1126 /science.aao1157.
[20] Christopher Finan, 2017, Drunks: An American history , Beacon, 41.
[21] Keith Humphreys, 2003, Circles of recovery: Self- help organizations for addic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n.d., “Alcohol’s effects on the body,” accessed September18, 2019, https:// www.niaaa.nih.gov/alcohol-health/alcohols -effects-body.
[23]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Alcohol Collaborators, 2018, “Alcohol use and burden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6: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 Lancet , 392, 1015–35,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8)31310-2.
[24] 感谢盖洛普公司的弗兰克·纽波特将这些数据发送给我们。
[25] Jay Bhattacharya, Christina Gathmann, and Grant Miller, 2013, “The Gorbachev anti- 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 mortality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 5(2), 232–60, http://dx.doi.org/10.1257/app.5.2.232.
[26] Pavel Grigoriev, France Meslé, Vladimir M. Shkolnikov, et al., 2014, “The recent mortality decline in Russia: Beginning of the cardiovascular revolu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40(1), 107–29.
[27] Robert T. Jensen and Kaspar Richter, 2004,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failure: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pension cri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1–2), 209–36.
[28] Angus Deaton, 2008, “Income,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2(2), 53–72.
在《帝国黄昏》 [1] 一书,历史学家史蒂芬·普拉特(又译裴士锋)讲述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就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部,以及今日的美国劳工阶层一样,当年的清朝也陷入了困境。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在勉力实现赢利,而其在19世纪30年代最赚钱的业务就是鸦片贸易,这些鸦片在印度生产并销往中国。出生在爱丁堡的医生威廉·渣甸是鸦片业务中最重要的商人之一。他的合伙人是苏格兰人马地臣,他们在1832年共同创办了怡和洋行。这家公司今天已更名为怡和控股,拥有40多万名员工,是全球300强公司之一。正如普拉特所说,渣甸、马地臣和其他鸦片贩子,“在家乡非但没有因其从事的行业受到玷污……反而成为他们各自社会中最受尊敬的成员” [2] 。
清政府则并不这样认为。它试图把英国人赶出除今天的广州以外的中国沿海地区,并取缔鸦片贸易。这种政策的执行十分涣散,时断时续。大清皇帝面临许多麻烦,正竭尽全力试图让一个行将崩溃的帝国免于瓦解。他需要镇压各地的起义,而鸦片贸易并不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1839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派往广东,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不仅相信人可以成功戒烟,还信奉今天所谓的药物辅助治疗成瘾。现在的曼哈顿唐人街矗立着一尊他的雕像,上面刻着“世界禁毒先驱”。在中国,他被视为民族英雄。
1839年6月,在皇帝的直接指示下,林则徐销毁了1000多吨英国鸦片(一年的鸦片供应),商人游说英国政府要求赔偿,这在政治上显然不可行,但派遣炮舰迫使中国人赔偿则是另一回事。同时,英国还可以借机迫使中国开放沿海的其他城市,不仅针对鸦片,还针对其他英国贸易品。当时,鸦片贸易并不合法。这种做法就好比因为美国缉毒局扣押了一批毒品,墨西哥的毒贩要求获得政府赔偿,但墨西哥政府拒绝用自己的资金支付,而是入侵得克萨斯州并要求美国人付款。尽管遭到严重批评,英国议会还是勉强批准了这场战争。此前不久,奴隶制刚刚在英国得到废除,许多人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的另一大罪行。国会议员似乎并非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极不道德,但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原则的坚守,首相墨尔本派海军远征东方。
这个故事还有不是特别为人所知的另一部分。东印度公司当时没有控制印度西部地区,那里的罂粟也很繁盛,东印度公司面临着孟买毒贩的激烈竞争,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巴斯 [3] 商人。来自他的鸦片供应帮助压低了中国的鸦片价格,使这一毒品从富人的奢侈品走向更广泛的人群。吉吉博伊将他从毒品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投入正途,这在今天仍然是常见的做法。他因慈善事业而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印度人。1858年,他成为勋爵,成为孟买的吉吉博伊男爵。这是一个可以世袭的头衔,最终传给了他的儿子。
那么渣甸和马地臣的命运如何呢?渣甸成为一名国会议员,于1843年去世,之后马地臣接替了这一职位。马地臣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还是英国最富有的人和最大的地主之一。1844年,他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买下了刘易斯岛。1851年,他受封为马地臣爵士,并成为刘易斯岛的首任男爵。在他购买刘易斯岛后不久,苏格兰发生了高地马铃薯饥荒,马地臣是一位慷慨的地主,他花费巨资救济灾民和改善岛屿设施。他还资助2337名(约占总人口13%)的岛民(或多或少自愿的)移居魁北克和安大略,并支付费用,使他们的牧师也能和他们同行。他正是因为这些慈善行为而获得男爵头衔。 [4]
用经济历史学家汤姆·迪瓦恩的话说,作家们经常把高地清洗 [5] 看作“人类需求对人类利益厚颜无耻的屈从” [6] 。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地主不同,马地臣似乎不应该受到这种谴责,但他以前的行为却难说无懈可击,这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受到政府支持的毒贩,即药品制造商,我们将在本章见识他们的行为。
在中年人中流行的三类绝望的死亡中,意外药物过量致死是人数最多,也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尽管在2017年,自杀和酒精相关死亡的人数相加后的人数更多。在第八章,我们探讨了自杀和酒精相关的死亡,以及它们与美国白人劳工阶层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阿片类药物及其造成的死亡。
阿片类药物可以指罂粟的天然衍生物,例如鸦片和吗啡,这些药物已被使用了数千年,在技术上被称为阿片(或鸦片)制剂。此外,阿片类药物也可指代具备全部或部分罂粟衍生物性质的合成或半合成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技术上被称为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目前通常用来指代上述两种物质。阿片类药物与70%的药物致死有关,包括单独使用以及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海洛因是一种阿片类药物,它于1874年被首次合成,在美国不能合法使用,尽管它在其他几个国家可用于医疗。
阿片类药物的强度通过与吗啡进行比较来测量。一毫克海洛因等于三毫克吗啡(或鸦片),因此它的吗啡毫克当量(MME)为3。当前流行的最重要的阿片类药物是羟考酮(MME 1.5),以缓释片的形式在市面上销售,即普渡制药生产的止痛药奥施康定。奥施康定在市面上有很多绰号,包括“乡村海洛因”,它在1995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另一个上市销售的是氢可酮(MME 1),药品名为维柯丁。此外,还有一个目前非常流行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MME 100),于1968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与海洛因(完全非法)或奥施康定(合法制造,但经常非法销售)不同,芬太尼既可合法获得,也可非法获得,其非法版本是从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
阿片类药物能够缓解疼痛。其实,它们不仅有止痛的功效,还能产生一种欣快感,促使人们希望重复获得。我们说“能”,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快感或疼痛得到缓解。身体会逐步产生对阿片类药物的耐受性,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的剂量控制疼痛或者达到同样的快感。使用者会发现很难停止使用它们,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对药物产生依赖,当他们试图停止使用时,将面临严重的戒断症状,包括呕吐、腹泻、出汗、失眠、抽筋,以及体验到在医学上所称的“寄生虫妄想”或“蚁走感”(没错,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感觉有蚂蚁或其他昆虫在皮肤下爬行。
阿片类药物也会导致成瘾,以及伴随成瘾而来的自我毁灭和家庭毁灭。即使仅仅到了药物依赖的程度,也会危及生命。人们的注意力将集中于维持自己的毒品消费,从而使工作、社交或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从按处方吃药到出现耐药性,再到药物依赖乃至上瘾,远非一个必然过程。海洛因在电影中经常被妖魔化,以致很多人认为注射一次就足以毁掉自己的生活。一般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但阿片类药物的确非常危险,通过阿片类药物长期缓解疼痛的风险非常大,而且效果也值得怀疑。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效果,奥秘就在于获得解脱和摆脱恐惧,以及消除疼痛,不必忍受蚁走感的折磨。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对疼痛管理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看到的,众多美国人曾经饱受疼痛折磨,现在依然如此。那些支持止痛的人宣称,美国对疼痛的治疗不够,于是大量效力强大的阿片类药物被派发到美国民众手中。2012年,医生开出的阿片类药物处方量已经足够所有美国成年人使用一个月。人们开始死于处方药物过量使用,虽然人数在开始时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6年,死于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人数上升至17087人,然后在2017年下降至17029人,也许这表明一个下降趋势的开始。 [7] 有些情况下,死者是接受处方的对象,但这些药物事实上经常会被转给他人,有时是通过黑市销售,有时则是通过盗窃行为。
2017年,在所有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中,来自医生处方的阿片类药物致死占了1/3,后者还占了当年70237例药物过量使用死亡总人数的1/4。这一总体数字高于每年死于艾滋病、枪杀或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数,比美国在越战中的死亡总人数还要多。2000—2017年,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的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数。同时,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过度使用还引发了次生的非法药物流行,因为普渡制药在后来推出了一种抗滥用型奥施康定,同时医生们也因为越来越意识到阿片类药物的危险而有所节制,或至少降低了合法药物供应处方的增长。
大多数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并不会死亡,也有一些死者可能是有意自杀的,因为意外过量用药和自杀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晰,甚至对受害者本人而言也是如此。 [8] 对应每一例死亡,都有30多例因为误用或滥用药物而需要去看急诊的病例,其中10例会因此入院。每一例死亡对应的滥用药物病例则达100余例。这些数字一直在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同步上升。2016年,近2900万名达到或超过12周岁的美国人自我报告称,在前一个月曾使用过非法药物(包括滥用处方药),同时94.8万人自我报告称,在前12个月内曾使用过海洛因。 [9] 鉴于这些都来自参与全国吸毒与健康调查的人的自我报告,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2015年,超过1/3的成年人(9800万人)服用过阿片类药物。许多雇主在雇用新员工之前会进行药检,因此,除了那些因药物依赖而无法工作的人之外,成瘾性药物的使用本身似乎也正在使人们远离劳动力市场。 [10]
和其他绝望的死亡一样,在阿片类药物死亡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与合法和非法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相关的死亡再一次主要发生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对白人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在意外药物过量死亡中的比例一直为9%,而死亡人口中的2/3最高只接受过高中教育。在2013年非法芬太尼进入美国之前,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基本上未被阿片类药物滥用荼毒,但在此之后,他们中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大幅增加。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主要是说英语的加拿大、英国(特别是苏格兰)、澳大利亚、爱尔兰,还有瑞典,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并且除了苏格兰之外,其他几个国家的死亡人数与美国相比微不足道。然而,阿片类药物在其他富裕国家也被广泛使用,通常是在医院中用于治疗癌症或术后疼痛,而社区医生或牙医很少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而且它们在长期治疗慢性疼痛中的使用频率也低得多。
制药公司从合法的阿片类药物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根据多个媒体报道(包括《洛杉矶时报》所做的调查性报道),萨克勒家族私人拥有的普渡制药公司已售出价值约300亿~500亿美元的奥施康定。最近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家族自身即获得120亿~130亿美元的利润。 [11] 非法毒贩(许多来自墨西哥)同样从中获利颇丰, [12] 但与这些人相比,合法药物生产商的优势是在日常经营中不会面临逮捕或暴力的风险。
医生们在这场流行病中也难脱干系,他们至少犯下了不谨慎地开出过量处方的错误,尤其是在这场流行病的早期。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的医疗制度造成的。对此类死亡的标准术语是医源性死亡,意思是“由治疗者导致”的死亡。这令人感到讽刺,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制度,美国的医疗制度不但未能阻止预期寿命的下降,反而实际上对预期寿命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看到的那样,其失职之处不只是对阿片类药物的不当处理。
纵观历史,人们一直用罂粟制品止痛和获得快感。提供这些制品的人的出发点往往是帮助他人,同时让自己获利,这两个目标并不一定互相矛盾。自由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帮助他人致富。但是,自由市场在医疗领域的运行总体而言并不太好,尤其是对于成瘾性药物,因为这些药物的使用者经常会做出明显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供应商若是能够让消费者对其产品上瘾,则将有利可图,因而双方的互惠互利很可能演变成利益冲突。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更有利于英国鸦片贩子的结果。
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赖特撰写了许多有关药物史的文章,他说,在美国内战中,联军士兵获得了超过1000万个鸦片丸和近300万盎司的酊剂和粉末鸦片。 [13] 战后,当时刚刚发明出来的皮下注射针(最初人们认为借助它可以让药物绕过消化系统而减少上瘾的机会)被广泛用于给退伍军人注射鸦片以止痛。考特赖特指出,“在整个医学史上,第一次可以对多种疾病进行接近即时性的症状缓解治疗。一支吗啡注射器已经千真万确地成为一根魔杖” [14] 。到19世纪末,吗啡和鸦片在美国随处可得,并被广泛使用,包括使用于儿童身上。吸毒现象在南方白人中尤其普遍,因为他们的世界在内战后变得一团糟。到20世纪末,拜耳公司成功合成海洛因并将其作为吗啡的非成瘾性替代品进行销售。于是更多的美国人染上毒瘾。而且,许多出现入睡困难的儿童被注射海洛因以帮助他们入睡。 [15]
最终,医学界重归正途,开始努力限制公众和医生使用阿片类药物。1914年,《哈里森麻醉品法》出台,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大规模阿片类药物流行的结束。该法案严格限制类阿片的使用和销售,10年后,海洛因被完全禁止。持有和销售阿片类药物成为犯罪活动,其使用也在绝大多数人中消失。可敬之人不再使用鸦片或海洛因治疗轻微的疼痛,也不再给有绞痛的婴儿喂食这种毒品。
那么,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怎么又会暴发了新一轮阿片类药物流行呢?人们忘记过去,甚至即使那些还记得过去的人,也可能认为已经事过境迁,这次会有所不同,过去的风险已经被安全地锁在过去。由于药物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利润,总会有人跳出来表示药物的风险被过分夸大了。人们当然也还没有消灭疼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慢性疼痛症状正在加剧,治疗(或不治疗)它对医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5年前,罗纳德·梅尔扎克提出痛觉的闸门控制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疼痛的理解。他在1990年所写的一篇题为《不必要疼痛的悲剧》的论文,雄辩地记录了疼痛的恐怖,并提出“事实上,当病人服用吗啡对抗疼痛时,很少出现上瘾现象” [16]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上瘾的风险无关紧要。然而,很多癌症患者长期存活,更多患者面临的,是手术后的巨大疼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慢性疼痛患者。到2017年,有5440万美国成年人被诊断患有关节炎,而关节炎只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更加普遍的许多疼痛状况之一。 [17]
从1990年左右开始,疼痛专家越来越多地呼吁人们更好地认识疼痛,并要求医生询问患者的疼痛程度。詹姆斯·坎贝尔医生在1995年美国疼痛协会的主席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把疼痛视为第五大生命体征”,这意味着医生应该像评估呼吸、血压、脉搏和体温一样,定期评估疼痛。坎贝尔还对区分癌症疼痛和非癌症疼痛,以及急性和慢性疼痛是否有用提出质疑。 [18] 美国疼痛协会于2019年6月关闭,成为21世纪阿片类药物之战的一个牺牲品。该协会面临指控,指其充当了制药公司的走卒(它对此予以否认),并因无力支付辩护律师费而宣告破产。 [19]
人们到今天仍然在激烈争论,服用阿片类药物来缓解疼痛到底是否像梅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无须担心上瘾的后果。梅奥医学中心的网站通常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它对此提供了矛盾的建议。在针对氢可酮的讨论中,它指出“长期使用氢可酮可能使其成为习惯,导致精神或身体上的依赖。然而,那些遭受持续疼痛的人不应该让药物依赖的恐惧阻止他们使用麻醉剂来缓解疼痛。当麻醉药被用于缓解疼痛的目的时,精神依赖(成瘾)不太可能发生” [20] 。不过,在梅奥医学中心网站的另一个区域刊登着一个更为谨慎的建议——“任何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人都面临逐渐成瘾的风险……开始阿片类药物的短期疗程仅仅5天之后,在一年后仍会继续服用阿片类药物的概率就会增加” [21] 。医生们希望帮助病人,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魔杖。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全科医生和牙医大量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用来治疗各种疼痛,特别是在1996年奥施康定推出之后。奥施康定据称带有12小时缓释机制,可以让疼痛患者彻夜安眠。不幸的是,在很大一部分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者中,疼痛复发和药物失效的时间远远短于12小时,许多医生对此的反应是,将服药的间隔缩短至8小时,或增大剂量。这种疼痛缓解和药物失效周期增加了滥用与上瘾的风险。
奥施康定的推出引发了疼痛患者看似无限的需求。大多数执业医生都需要面对巨大的时间和费用限制,这使得开口服药片处方远比进行昂贵和耗时的治疗更具吸引力。早期的疼痛治疗标准是跨学科治疗,即使用药物的组合,例如危险性较小的非甾体抗炎药,如(非处方药)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或萘普生,或者(处方药)塞来昔布,然后辅以咨询、锻炼、瑜伽、针灸和冥想,所有这些都很难在标准的医生预约流程中做到。病人满意度调查也变得很普遍,而阿片类药物在这些调查中的表现良好。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个世纪前对患有绞痛的婴儿和给他们使用海洛因的父母进行调查,他们的满意度也会很高。关节炎患者很容易会从初级保健医生那里拿到阿片类药物处方,牙医也会给病人开出可以服用多日的阿片类药物,来急诊室治疗各种损伤的患者也全会带着阿片类药物离开。
或许医生可以评估哪些病人存在成瘾风险,但这不可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也不可能在一个许多患者没有私人医生,也没有统一诊疗记录的系统中完成。甚至可能在病人死于处方药物时,医生都一无所知。当他们收到通知信函后,许多医生减少了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 [22]
在上一次流行病一个世纪后,一场阿片类药物滥用、成瘾和死亡带来的医源性流行病再次出现。戴维·考特赖特告诉记者兼作家贝丝·梅西,“我有生之年见到了不少让我吃惊的事情,比如互联网,又或者体面的女孩儿也会文身,但我不得不加上一件让我真的无比震惊之事。我已经64岁,不得不承认,我从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会见证另一次医源性阿片类药物成瘾泛滥的大潮” [23] 。
随着宗教信仰的式微,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20世纪90年代初,死于药物过量使用的人数开始上升,并且这一上升势头在2000年后开始加速。2000年,意外药物过量使用致死人数超过14000人。区分特定死亡案例具体是由哪种药物的过量使用所致非常复杂。有为数不少的药物过量使用死亡病例涉及不止一种药物。单独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24] 不太可能致死,但它们与阿片类药物或酒精混合后则会变得致命。此外,死亡证明上往往不会记录致死药物的详细资料,相关的栏目往往记录为“未明确”。2000年,在所有意外过量药物使用的死亡案例中,1/3到1/2涉及阿片类药物(主要是处方药),具体数量取决于我们如何归因“未明确”麻醉类药品造成的死亡。根据记录,海洛因这一长期存在的罪魁祸首在当年造成1999例死亡。2011年之前,死亡人数的增加由处方类阿片类药物推动,特别是那些基本成分为氢可酮和羟考酮的阿片类药物。2011年,普渡制药公司更改了奥施康定的配方,以避免药物滥用。药品说明中带有警告,要求使用者必须遵医嘱服用,但这些明确公示不该做什么的警告很容易起到反作用,反而详尽地指导了使用者如何将缓释药片变成可立即带来快感的药品,或者如何将其变成可注射的毒品。 [25] 2011年,处方类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配方的更改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医生们不断提升的意识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意识到在这场流行病中扮演的角色,医生随意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的行为也有所收敛。事实上,配方的更改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死亡,因为它会迫使使用者转向相对更不安全的非法毒品。同时,由于更改配方,普渡公司即将到期的专利得以续期,该公司更关心的可能是这一点,而非拯救生命。
无论如何,时至2011年,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非法海洛因,一种几乎完美的羟考酮替代品很快开始填补空缺。处方药导致的死亡被海洛因导致的死亡取代,推动药物过量使用致死的总人数继续攀升。毒贩在止痛诊所门外守候着遭医生拒绝续开新药的病人。一些人在黑市购买(转售的)奥施康定,直到发现更便宜和更强效的海洛因。这种行为也更危险,因为非法出售的毒品质量根本无法保证。与此同时,来自墨西哥的新供应商大量提供高质量的黑焦油海洛因,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转换起来相当容易。奥施康定处方被挪用出售,以换取和吗啡等效剂量的海洛因,从而令使用者既能保证摄取足够的毒品剂量,又能在交易中获利。 [26]
尽管海洛因致死人数不断增加,但其很快被芬太尼致死的人数超越。2017年,芬太尼致死人数增至28400人。芬太尼的崛起反映了它强大的效力以及进口的便利性,因为它的有效剂量远远小于海洛因,而且可以与多种毒品混合使用,包括海洛因、可卡因、快球 [27] 以及冰毒(甲基苯丙胺)和Goofball(傻瓜) [28] ,从而提供更强效的吸毒快感。 [29] 海洛因和非法芬太尼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处方类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人发现他们的需求越来越难以被满足。但这些新型毒品的存在似乎已经导致它们自身的大流行,也就是说,服用者已经不是从处方类阿片类药物开始,进而转向这些毒品,而是从一开始服用的就是这些非法替代品。减少可卡因和海洛因,转而使用芬太尼是导致非洲裔美国人药物过量使用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之一。2012年后新增的中年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中,死亡证明将芬太尼列为死因的人数达到增加人数的3/4。 [30]
熊熊大火已经突破防火线。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某个毒贩的客户因药物过量死亡,其他客户就会避开他,但非正式的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那些对阿片类药物上瘾的人实在是太渴望虚空麻木的感觉了,以致他们会将出现此类死亡视为供应源值得信赖的证据,因为这表明该毒贩提供的东西货真价实。事实上,这并不是表明此类死亡应归属于自杀的唯一证据。一种名为纳洛酮的药物具有神奇的功效,可以把那些因过量服用药物而濒临死亡的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然而,来自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报告显示,他们曾多次向同一人施用纳洛酮,有时甚至是在一天之内就多次施用。这表明这些人要么一心求死,要么除了满足毒瘾之外已经不在乎任何东西,即使这意味着让他们送命也无所谓。他们已经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毒瘾。
提到“流行”一词,人们很容易会将其与天花大流行,或者1918—1919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流感相比较。在阿片类药物的流行中,媒介不是病毒或细菌,而是下列方方面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药物并积极推动其销售的制药公司;阻止美国缉毒局对有意过度开具处方的医生提出起诉的国会议员;作为监管机构的美国缉毒局屈服于游说者的要求,没有弥补法律漏洞,而是允许从塔斯马尼亚罂粟种植场进口原材料,为这一流行病提供了弹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阿片类药物上市,而没有考虑这样做带来的广泛社会后果,它还同意了制药公司的要求,批准了标签更改,从而大幅度扩大了阿片类药物的用途,并为药厂带来丰厚利润;那些漫不经心地开出超量处方的医疗界人士;来自墨西哥等国的药贩子在医学界开始控制阿片类药物处方时接棒,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药品。在这场流行病中,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药物的供给方通过使人上瘾并送命而赚取巨额利润,政治权力则对犯罪者施以保护。一旦人们开始使用阿片类药物,就仿佛是已经感染病毒。虽然他们有可能幸存,但他们也有可能死亡。没有人应该怀疑供给在这场流行病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正是因此而做出了我们的论述——但是,只谈论供给并不能了解事实的全貌。
为什么这种流行病在美国如此严重,但在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却几乎未见踪影呢?即使在美国,某些阿片类药物,例如维柯丁,甚至芬太尼,也都是早已上市的药物。其他国家也普遍使用阿片类药物来治疗术后疼痛和癌症相关疼痛,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长期使用海洛因止痛,虽然海洛因在美国被禁止使用。是什么阻止了这些药物从预期用途扩散到普罗大众呢?
此外,为什么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很少死于药物过量使用(在死于过量用药的人口中,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占90%)?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受伤,或者从事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疼痛的高风险工作,因此他们需要服用阿片类药物止痛,但这绝非故事的全部。关节炎是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的主要症状之一,而这种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与年龄相关,如果老年人更容易获得阿片类药物,他们并不会因此丧命。在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拥有学士学位的60岁白人人口中,有一半人报告他们经受着背痛、颈痛或关节痛的折磨,而在没有学士学位的60岁白人人口中,这一比例为60%。如果说那些经受疼痛的人需要服用阿片类药物,而药物处方会让一部分人上瘾,并且在上瘾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死亡,那么上面的比例差异完全无法解释,为何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药物过量使用的死亡率是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7倍。也许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疼痛更适合服用阿片类药物,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下面是我们针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的讨论和解读。
尽管在阿片类药物流行这出戏里,所有角色都因为不道德和贪婪的行为而难辞其咎,但我们仍然认为,批评医生和毒贩是一丘之貉是不对的。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医生开始做“卖药生意”,在不做检查甚至不看患者的情况下,为了金钱(或性)而出售处方。 [31] 这些医生中的许多人现在(或在过去)已经进了监狱。不过,腐败的医生毕竟是少数,鉴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学界的共识,医生们有充分的理由给患有疼痛症状的病人开具阿片类药物,而没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我们猜测,使用适当剂量的阿片类药物来缓解急性疼痛,这样做本身不大可能导致成瘾,这同样也适用于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但是,使用阿片类药物来长期治疗慢性疼痛是否合适则是另一回事。显然,例外情况也存在,即药量适当的短期处方也会导致成瘾。其中一个例子是特拉维斯·里德尔,他居住在巴尔的摩,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由于左脚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被压碎,他经历了多次手术,随后医生给他不断开出剂量越来越大的阿片类药物处方用来止痛,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了药瘾,而在此过程中,给他开止痛药处方的医生一点忙也没有帮。 [32] 他的故事值得我们牢记并作为警示,提醒我们可能会发生什么。即使天时、地利、人和俱全,药物成瘾也很难戒掉。
然而,如果说任何人仅注射一针海洛因就会立即、不可避免地上瘾,显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据估计,今天美国每天或几乎每天都有大约100万人使用海洛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死亡,而且实际上还过着正常生活。很多人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地戒掉了毒瘾,还有很多人依靠自己、医疗机构或社会支持而成功戒毒。
尼克松当政时期曾有报道称,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蒂尔和摩根·墨菲在1971年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时发现,大量美国军人吸食海洛因。尼克松立即宣布海洛因成瘾是美国首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军人可能会被迫接受尿检,结果与士兵们自己的报告一致,显示34%的人曾吸食海洛因,多达20%的人已经上瘾。令调查人员吃惊的是,还有38%的人吸食鸦片(外加超过90%的人喝酒,以及75%的人使用大麻)。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都必须首先戒毒和通过尿检才会被允许回国,这成为他们戒毒的强大动力。这个项目被称为“金流行动”,那些退伍军人一回国就被追踪。结果显示,回到美国后,只有12%的人在三年内再度染上阿片类药物毒瘾,多数在越南服役期间吸毒的军人只染上了暂时性的毒瘾。也许针对他们的“排毒”行动获得了成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算是意外之喜,因为这比通常情况下的戒毒成功得多。这还可能是因为在战斗的压力下,鸦片和海洛因为士兵提供了某种解脱。不过,大多数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军人是在抵达越南后不久就开始吸毒的,而那些经历过更多战斗的军人并没有更多地染上阿片类药物毒瘾。
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来自李·罗宾斯的描述,他是参与调查的人员之一,我们上面的故事正是基于他对事件的记录。他表示,这些军人之所以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因为“他们表示这样做令他们感到愉悦,并使服役生活变得舒服一点儿” [33] 。他们服用阿片类药物并不是为了让战斗风险变低,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处于吸毒后飘飘欲仙的欣快感会让他们在战斗中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们纯粹是因为太过无聊而丧失了理智。当他们回到家乡,脱离了军队环境,有了其他享乐方式时,他们的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此时即使没有毒品,也可以忍受。环境因素非常重要,再加上这些药物在越南异常便宜。总之,触发这些军人在越南日常使用毒品的因素在其家乡并不存在,而且由于他们是在越南,而不是在家乡戒的毒,戒毒—复吸的怪圈也因为地理原因而被打破。 [34] 罗宾斯认为,人们对海洛因上瘾的普遍看法源于一个事实,即许多研究都是针对在一开始就更容易上瘾的特殊人群进行的,而不是针对在越南服役的更广泛的军人群体的。
一定是人们生活中有某种东西驱使他们通过药物寻求快感或麻木,而不是药物本身的某些固有属性会让所有接触到它们的人上瘾。如果不了解吸毒者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在现在和在过去如何影响吸毒者,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吸毒现象。正如一位医生对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会造成很大影响。 [35] 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们将对劳工阶层分崩离析的生活现状进行分析。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医生会直接使自己的病人上瘾。但是,他们可能太愿意相信,阿片类药物能比早期的跨学科方法提供更成功的长期止痛效果。事实上,这样的证据几乎无法找到,而且我们再次强调,全国层面的疼痛症状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不是下降趋势,而考虑到已经开出的巨大数量的阿片类药物处方,如果这些药物真正有效,疼痛现象本应该下降。医生们面对病人的痛苦做出了正常的反应,但他们可能并没有考虑其处方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成本。他们还面临制药厂商通过一些渠道施加的巨大压力,包括直接营销和资金充足的公众“教育”宣传,以及代表疼痛症患者的宣传组织,其中一些组织接受了来自制药厂商的大笔捐款(这些虚假或被渗入的草根协会有时被称为“草根营销”组织)。医生开出远超实际需要量的强效阿片类药物处方,有时给那些根本无此需要的病人开出阿片类药物,而这些用不完的药物则可能进入黑市,这本身就可以证明阿片类药物不一定致瘾。有些医生还为那些本来就是为了转售,而不是自己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病人开了处方。这些病人会四处寻医,直至找到愿意给他们开处方的医生。医生努力做到不给此类病人开药,但很难想象他们能够辨别病人的意图,特别是考虑到他们面临的时间压力。此外,那些有可能滥用或者有过滥用史的病人可能真的正在经受疼痛。虽然医生们被要求对药物滥用进行管理和预防,但在他们目前的工作环境中,这个要求实际上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一些评论家认为,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对这一流行病负责,因为医疗补助计划的扩张使阿片类药物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但这种指责与阿片类药物流行病的时间不符,因为在医疗补助计划推行之前,这一流行病已经全面暴发。相比之下,在为阿片类药物滥用障碍患者提供负担得起的治疗方面,医疗补助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后,医疗补助得到扩大的州的治疗水平也获得大幅提高。 [36]
药物的生产商则采取各种直接手段,或间接通过处方福利经理,尽可能增加销售额和利润,哪怕药物已经明显被滥用。例如,在两年的时间里,900万粒药物被发送到仅有406人的西弗吉尼亚州克米特城的一家药房。根据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2007—2012年,“药物经销商向西弗吉尼亚州运送了超过7.8亿粒氢可酮和羟考酮” [37] 。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调查,当负责制止此类滥用行为的美国缉毒局试图采取行动时,国会通过了2016年的《保障病患获得有效药物执行法案》,其规定有效地阻止了美国缉毒局采取制止药物泛滥的行动。 [38] 唐纳德·特朗普随后提名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汤姆·马里诺担任他的禁毒负责人,负责该法案的执行。随后,《60分钟》和《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揭露,马里诺多年来一直代表制药业努力推动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迫使他在公众的愤怒声讨中辞职。调查性新闻报道还揭露了一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反水者”——林登·巴伯,他以前是美国缉毒局的高级律师,后来转换门庭,为制药行业提供顾问服务,并帮助起草了该法案。
美国最知名的制药公司之一强生公司是美国大部分阿片类止痛药的原料供应商,其子公司塔斯马尼亚生物碱公司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拥有大型罂粟种植农场。记者彼得·奥德丽·史密斯报道,美国缉毒局对这些情况非常了解,但应制药业游说者的要求,拒绝修补法律漏洞。 [39] 就在美军轰炸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鸦片产地之时,强生公司在塔斯马尼亚合法地为美国阿片类药物生产商提供原料。2019年8月,强生公司因被判定对阿片类药物泛滥负有责任,而被勒令向俄克拉何马州支付5.72亿美元罚款。预计该公司将对此提出上诉,不过它同时还面临正在审理中的其他诉讼。 [40]
我们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它们证明了民主政治在解决阿片类药物流行上的失败。马里诺的选区受到阿片类药物的严重影响,上面提到的法案的一个提案人——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所在的田纳西州也同样深受其害,然而,他们却反对有效的监管。一切向钱看和以企业为先的观念取代了为那些深陷毒瘾,甚至濒临死亡的人发声的义务。丑闻并没有阻止马里诺在2018年再次当选众议员,不过他在2019年1月因健康状况不佳辞职。布莱克本也再次当选,她现在是田纳西州的资深参议员。参议员奥林·哈奇是制药行业的老朋友,并得到后者的长期赞助,他则帮助法案顺利过了美国缉毒局这一关。42年来,哈奇一直代表犹他州担任参议员,该州从1999年到法案正式通过的2016年期间,药物致死率增长了足足7倍。
如果没有医生的不负责任,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程序瑕疵,或者没有制药行业不计任何人道成本地追求利润,这场流行病就不会发生。今天,在美国法庭上,近2000个市政当局正在追究制药公司高管的责任并要求赔偿,从而使这个行业肆无忌惮的做法被广泛曝光。其中一个诉讼于2019年5月结案,法庭判决对止痛药制造商Insys Therapeutics的5名高管提出的联邦敲诈勒索指控成立,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对医生行贿,让他们为不需要芬太尼的患者开具处方。 [41]
我们认为,虽然这些不当行为给这场流行病火上浇油,并推动形势恶化,但它们并非导致这一流行病发生的先决条件。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者,其中数百万已经成为阿片类药物滥用者或上瘾者,成为在曾经兴旺繁荣的城镇街道上行走的僵尸。这些人的生活在他们开始嗑药之前已经分崩离析,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持。诚然,这一流行病的供给方无疑很重要,无论是制药公司,还是它们在国会的支持者,或者不负责任乱开处方的医生,但我们应该看到,同样十分重要的还有需求方,即白人劳工阶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他们本已痛苦不堪的生活成为一片沃土,供贪婪的企业、功能失调的监管体系,以及存在缺陷的医疗制度肆意妄为。阿片类药物在其他国家并没有流行,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摧毁自己的劳工阶层,也因为它们的制药公司得到更好的监管,它们的政府也没这么容易被追逐利润的企业左右。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美国经济如何从为普通民众服务转向为企业、其管理者和所有者服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讨论。政府和法律已经成为共犯。本章关于阿片类药物的阐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让我们看清这一过程。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重点讨论财富如何向上再分配,即从劳动人口转移到公司及其股东的再分配机制。美国的医疗行业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并且已经超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和分销商的范围。这些人的行为当然并不是普遍行为,而且正如我们所述,他们已经因其行为而面临司法诉讼,但利用市场势力实现向上的再分配,掠夺拥有很少财富的大量普通百姓,并分配给拥有大量财富的少数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医疗领域的现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普遍现状。受益者不仅包括富有的大股东,还包括许多高教育程度的精英人士,他们间接在退休基金中持有股票,并从公司利润增加的所有行为(包括降低工人工资)中受益。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在蚕食劳工阶层的生活基础,包括高薪和一份好工作,并且在导致绝望的死亡泛滥上起到关键作用。阿片类药物的故事符合这个大主题,但它更加触目惊心,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情况,即企业如何从人们的死亡中直接受益。
我们并不认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被制药行业掌控,尽管它在阿片类药物的审批,尤其是在奥施康定的批准上的确出了很大的问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有公众)非常尊重证明药物有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但即使在这些试验中,阿片类药物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奥施康定的对照组(随机选择的未使用药物组)在试验的早期阶段,即所谓开放性试验阶段,曾服用过奥施康定。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那些不能耐受药物的人排除在试验之外。 [42] 在此类试验的两个阶段之间,会有一个“洗脱期”,以确保药物已经在此期间被清洗出病人的身体。对于奥施康定(或任何成瘾性药物)而言,此类试验的危险在于,如果洗脱期不够长,在不再使用药物的对照组中,某些人可能出现戒断症状,而这会使他们的状态看起来不如那些进入治疗组,并再次接受药物的人。此外,由于在早期的开放性试验阶段排除了那些不能耐受药物的人,这意味着试验将低估药物在更广泛人群中发生问题的概率,而在药物上市之后,这些人都有可能收到这种药物的处方。同时,在开展药物试验之前,制药公司是可以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讨论试验设计的各个方面的。
总而言之,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一个小组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试验和批准过程仅仅着眼于这些药物对个人的作用,而忽略了向社会推出一种强效、高度成瘾药物将导致的更广泛影响,这种观点显然非常正确。 [43]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能够预见批准奥施康定会造成的全部后果,并不现实,但是一个未能考虑到批准该药物对公众健康影响的制度性失败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毕竟,它实质上给合法海洛因的销售盖上了政府的批准章。
阿片类药物的故事充分揭示了资本的力量,它能阻止政治保护普通公民,甚至保护他们免于死亡。至少直到2019年,在公众高涨的愤怒情绪终于改变人们的看法之前,那些因此而发了大财的人既没有被排斥,也没有被谴责,而是被公认为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普渡制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萨克勒家族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博物馆、大学和各类慈善机构当中,不仅在美国,还在英国和法国。在奥施康定被研制出来前已经去世的阿瑟·M.萨克勒对许多机构提供了大笔捐赠,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史密森尼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萨克勒家族的财富来自其开发出当今美国普遍使用的药品广告和销售体系。借用一位评论人士的话来说,“推动制药行业陷入今天这场灾难的大多数可疑做法都可以归咎于阿瑟·萨克勒” [44] 。
阿瑟·萨克勒的兄弟雷蒙德和莫蒂默,以及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是普渡公司在奥施康定上市和营销期间的掌舵人。1995年,雷蒙德和莫蒂默双双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为爵士,这与一个半世纪前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45] 就像18世纪贵族佩戴的假发一样,香水只能掩盖,但不能消除道德败坏的恶臭。 [46]
今天,女王不太可能授予这类人这一荣誉。上面列出的大多数组织也已经停止使用萨克勒的名字,它们中有些是在多年抵制之后才做出这一决定的。此外,还有一些组织宣布,它们将不会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款。
制药公司已经从这场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它们现在正准备从治疗中获利。目前还没有简单或可靠的药物治疗方法来治疗药物上瘾,现有的最好方法是药物辅助治疗(MAT),即让那些上瘾的人在戒毒期间使用不同的阿片类药物(美沙酮或丁丙诺啡)来控制他们对毒品的渴求。虽然我们怀疑MAT的效果很可能被夸大,因为其有效性的证明只来自那些承认自己上瘾并寻求治疗的患者(很多瘾君子并不会这么做),还因为相当一部分人会中途退出MAT,但无疑MAT比单纯的禁药治疗法更有优势,因为后者是导致复吸过量死亡发生的重要原因。那些已经戒毒一段时间的人会失去对药物的耐受性,并可能在复吸时因为使用与戒毒前相同的剂量而导致药物过量死亡。即便如此,看到制药公司和它们的盟友如此大力推广MAT,以便它们既可以通过引发流行病获利,又可以通过治疗同样的流行病赚钱,仍难免令人作呕。事实上,2018年夏,普渡制药公司获得了可用于MAT的一种药物的专利,使其看上去有望再次重演奥施康定的成功。这就好像给供水系统下毒的人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或者使他们生病之后,又来索要一大笔赎金,提供解药来拯救幸存者一样。
在我们撰写本书的时候,那些针对制药公司蜂拥而至的诉讼又会取得怎样的效果呢?它们无疑将永久性地减少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供给,供给已经开始减少。随着对毒品的需求从合法来源转向非法来源,它们对减少非法毒品的使用几乎没有作用,甚至可能增加非法毒品的使用。巨额和解协议可能会使包括普渡在内的一些制药公司破产,尽管其他一些公司在过去曾凭借其更强的资金实力,或通过提高其生产的药品价格,轻松地支付了巨额罚款并脱身。就像烟草公司曾经做过的那样,普渡目前正试图保留对其欧洲子公司萌蒂制药的控制权,以便继续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展业务。同时,那些收取罚款的州和地方当局能否用好这些钱也有待观察。此前曾有过与这种情况类似的例子,而结果并不令人那么放心。1998年,美国与多家烟草公司之间达成了烟草大和解协议,从那以后,各州从这些公司手中获得数千亿美元——这些钱实际上全部来自烟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贫穷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但收到的钱几乎全部被用于一般性收入,从而减少财产税和所得税。就阿片类药物而言,活下来的公司将有能力提高产品价格,使医疗成本变得更高,因此,历史将再次上演,赢得诉讼胜利的州未来收取的罚款费用,最终将由那些支付医疗费用或医疗保险费用的普通人承担。这些罚款显然并不会对激励制药公司改变其行为起到多大作用,只有判定高管行为不当并承担刑事责任,才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后面这类判决虽然并非没有,但非常少见。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好处经常得到传扬,也确实当之无愧,包括它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之物的能力,它对创新的激励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我们对此完全同意。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包括制药业,并不像一个自由市场。存在赚钱的公司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自由市场竞争。相反,这些受到高度监管的公司主要关注的是寻求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保护性监管,以保证获取利润,并以在自由市场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方式限制竞争。我们当然不是要鼓吹一个美国医疗制度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我们只是想指出,我们现在拥有的制度并不能被称为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一个从腐蚀自由市场竞争中赚取超额利润的行业竟然能够指责其批评者,称对方为自由市场的反对者,这实在令人极其愤怒。对偷窃行为的谴责绝不是反对市场经济。其他国家已经制定一系列医疗制度,各自有其长处和短处,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为了杀人,也没有一个支持“人类需求对人类利益厚颜无耻的屈从” [47] 。
如果我们允许阿片类药物贸易带来的利润腐蚀美国,就像一个半世纪前的中国一样,在后世被视为百年屈辱和衰落的开端,那无疑将是一场悲剧。
[1] Stephen R. Platt, 2018, 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 Knopf.
[2] Platt, 202.
[3] 巴斯人是一个亚洲少数族群,主要指生活在印度、信仰祆教的信徒。鸦片战争前后巴斯商人在广州口岸的贸易十分频繁。——译者注
[4] Richard J. Grace, 2014, 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 ,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5] 高地清洗,在盖尔语中被称为“盖尔人驱逐”,指1750—1860年,在苏格兰发生的大量佃农从高地和群岛被驱逐的事件。——译者注
[6] Tom M. Devine, 2018, The Scottish Clearances: A history of the dispossessed, 1600–1900 , Allen Lane, 3.
[7]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2019, “Overdose death rates,” revised January,https://www.drugabuse.gov/related-topics/trends-statistics/overdose-death-rates.
[8] Amy S. B. Bohnert, Maureen A. Walton, Rebecca M. Cunningham, et al., 2018,“Overdose and adverse drug event experiences among adult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ddic tive Behaviors, 86, 66–72.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一级创伤中心接受调查的药物使用过量患者中,有21%的患者表示不确定自己的意图。
[9]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7, Key substance use and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2016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 HHS Publication No. SMA 17-5044, NSDUH Series H-52, Center for Behavioral Statis-tics and Quality,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samhsa.gov/data/sites/default/files/NSDUHFFR1-2016/NSDUH-FFR1-2016.pdf.
[10] Dionissi Aliprantis, Kyle Fee, and Mark Schweitzer, 2019, “Opioids and the labor marke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Working Paper 1807R; Alan B. Krueger,2017, “Where have all the workers gone? An inquiry into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 Fall, 1–87.
[11] Jared S. Hopkins and Andrew Scurria, 2019, “Sacklers received as much as $13 billion in profits from Purdue Pharma,” Wall Street Journal , October 4.
[12] Sam Quinones, 2015, Dreamland: The true tale of Ameri ca’s opiate epidemic ,Bloomsbury.
[13] David T. Courtwright, 2001, A history of opiate addiction in Ameri c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14] Courtwright, loc. 604 of 4538, Kindle.
[15] Beth Macy, 2018, Dopesick: 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 ca , Hachette.
[16] Ronald Melzack, 1990, “The tragedy of needless p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62(2), 27–33.
[17] Dana Guglielmo, Louise B. Murphy, Michael A. Boring, et al., 2019, “Statespecific severe joint pain and physical inactivity among adults with arthritis — United States, 2017,”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19(68), 381–87, http://dx.doi.org/10.15585/mmwr.mm6817a2.
[18] James M. Campbell, 1996, “American Pain Society 1995 Presidential Address,”Journal of Pain , 5(1), 85–88.
[19] Chris McGreal, 2019, “US medical group that pushed doctors to prescribe painkillers forced to close,” Guardian , May25, https:// 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9/may/25 /american - pain- society- doctors- painkillers; Damien McNamara, 2019,“American Pain Society officially shuttered,” Medscape, July2, https:// 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15141.
[20] Mayo Clinic, 2019, “Hydrocodone and acetaminophen (oral route),” last updated October1, https:// www.mayoclinic.org/drugs-supplements/hydrocodone-andacetaminophen -oral-route/description/drg-20074089.
[21] Mayo Clinic Staff, 2018, “How opioid addiction occurs,” Mayo Clinic, February 16, https:// 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prescription-drug-abuse/in-depth/how-opioid -addiction-occurs/art-20360372.
[22] Jason Doctor, Andy Nguyen, Roneet Lev, et al., 2018, “Opioid prescribing decreases after learning of a patient’s fatal overdose,” Science , 361(6402), 588–90.
[23] Macy, Dopesick , 60.
[24] 苯二氮卓类药物包括地西泮(安定)、氟西泮(氟安定)、氯氮卓、奥沙西泮和三唑仑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主要用于抗焦虑、镇静催眠、抗惊厥、肌肉松弛和安定。——译者注
[25] Quinones, Dreamland .
[26] Quinones.
[27] 快球指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混合制剂,用于静脉注射。——译者注
[28] Goofball是一种冰毒和海洛因的混合毒品,因为吸毒者表示吸食后会感到“傻,但是幸福”而得名。——译者注
[29] Scott Gottlieb, 2019, “The decline in opioid deaths masks danger from designer drug overdoses in US,” CNBC, August22, https:// www.cnbc.com/2019/08/21/decline-inopioid -deaths-masks-new-danger-from-designer-drug-overdoses.html.
[30] 2012—2017年,年龄在25~64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按年龄调整的每10万人中死亡人数增加了20.8个。而同一时期涉及其他合成类(非海洛因,非美沙酮)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每10万人中死亡人数增加了15个。
[31] Anna Lembke, 2016, Drug dealer, MD: How doctors were duped, patients got hooked, and why it is so hard to stop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 Travis N. Rieder, 2016, “In opioid withdrawal, with no help in sight,” Health Affairs 36(1), 1825.
[33] Lee N. Robins, 1993, “Vietnam veterans’ rapid recovery from heroin addiction:A fluke or a normal expectation?,” Addiction , 88, 1041–54, 1049.
[34] 我们感谢丹尼尔·维克勒针对本章所做的讨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维克勒的想法在制订驻越南美军戒毒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5] Ken Thomp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13, 2018.
[36] Benjamin A. Y. Cher, Nancy E. Morden, and Ellen Meara, 2019, “Medicaid expansion and prescription trends: Opioids, addiction therapies, and other drugs,” Medical Care , 57(3), 208–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375792/; Andrew Goodman-Bacon and Emma Sandoe, 2017, “Did Medicaid expansion cause the opioid epidemic?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it did,” Health Affairs, August23, https:// www.healthaffairs.org/do/10.1377 /hblog20170823.061640/full.
[37]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US Congress, 2018, Red flags and warning signs ignored: Opioid distribution and enforcement concerns in West Virginia , December19, 4, https://republicans -energycommerc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2/Opioid-Distribution-Report -FinalREV.pdf.
[38] Brit McCandless Farmer, 2019, “The opioid epidemic: Who is to blame?,” 60 Minutes Overtime, February24, https:// www.cbsnews.com/news/the-opioid-epidemicwho-is-to-blame - 60- minutes/ ; Scott Higham and Lenny Bernstein, 2017, “The drug industry’s triumph over the DEA,”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15.
[39] Peter Andrey Smith, 2019, “How an island in the antipodes became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licit opioids,” Pacific Standard , July 11, updated July 24, https://psmag .com /ideas /opioids-limiting-the-legal-supply-wont-stop-the-overdose-crisis.
[40] Katie Thomas and Tiffany Hsu, 2019, “Johnson and Johnson’s brand falters over its role in the opioid crisi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7.
[41] District of Massa chu setts, US Attorney’s Off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2019, “Founder and four executives of Insys Therapeutics convicted of racketeering conspiracy,” May 2, https:// www.justice.gov/usao-ma/pr/founder-and-four-executivesinsys-therapeutics-convicted -racketeering-conspiracy.
[42] Lembke, Drug dealer, MD .当然,一旦药物获批,接受处方时就不会再进行这样的排除,因此,接受药物治疗的人群与接受药物试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43]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7, Pain management and the opioid epidemic: Balancing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benefits and risks of prescription opioid use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https://doi.org/10.17226/24781.
[44] Allen Frances, quoted in Patrick Radden Keefe, 2017, “The family that built an empire of pain,” New Yorker , October 23.
[45] Keefe.
[46] 我们感谢约翰·范·雷恩的这句箴言。
[47] Devine, Scottish Clearances , 3.

★★★
★★★
绝望的死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集中暴发,而且这种流行病正在拉大那些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寿命差距。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未过多讨论金钱(或缺乏金钱)的影响,以及收入或贫困在这一流行病中扮演的角色。即便对那些并不是绝对贫穷的人而言,收入较高的人也会活得更久, [1] 而且有证据表明,受教育程度也很重要,甚至在收入相同的人口中也是如此。 [2] 在美国,金钱可以买到更好的医疗,此外,如果你不必整天担心如何支付汽车修理费或儿童保育费,或者某个特别寒冷的冬天不期而至的高额取暖费,你的生活无疑会更轻松。经济上的焦虑会驱走生活中的快乐,给人们带来压力,并且往往会引发疼痛和健康问题。如果说金钱对健康没有任何有益影响,显然不合情理,尽管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财富与健康的关系,比如不良的健康状况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或教育对健康和财富的影响,以及童年的环境可能为成年后的健康和财富奠定基础。
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远不如欧洲和其他富裕国家完善。由于缺乏社会福利,人们拥有努力工作和挣钱的强劲动力,这对那些有能力的人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工作的人而言,则是灾难性的。同样不同于其他富裕国家,美国有数百万赤贫人口,他们的生活条件之恶劣,堪比非洲和亚洲的穷人。 [3] 在试图解释美国特有的死亡流行病时,贫困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在有关绝望的死亡和美国人总体糟糕的健康状况的讨论中,收入不平等经常被提到。美国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因此,这种不平等便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理由,用以解释美国在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的例外性。贫困和不平等被视为双重诅咒,通常(但往往并不准确地)被视作各种弊端之源,它们不仅被认为是造成健康状况欠佳和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还被指责破坏了民主治理,使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经济不稳定,削弱信任和幸福感,甚至刺激肥胖症的增长。 [4] 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贫困可能更加难以承受。穷人在不得不承受自己的贫困之余,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人过上远超温饱的富足生活。我们在本章中将充分讨论这种不平等现象。我们认为,绝望的死亡和收入不均显然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它们并非是从不平等直接走向死亡的简单因果关系。相反,权力、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深层力量既导致了绝望的死亡这一流行病,又带来了极端的不平等。不平等和死亡是摧毁白人劳工阶层的这些力量共同导致的后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均就像空气污染或致命的辐射,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会使每个人都受到毒害,无论贫富。我们对此不能苟同。首先,美国收入不均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急剧恶化,而当时恰逢死亡率迅速下降、预期寿命迅速上升(见图1-1)。此外,尽管美国某些州的平等状况远逊于其他州,但在这些平等程度较低的州,绝望的死亡流行病并不比其他州严重。新罕布什尔州和犹他州是美国收入不均程度最低的两个州,但这两个州同样受到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的沉重打击,其程度远远高于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尽管后两个州是美国收入不均程度最高的州。
经济大衰退始于2008年,其标志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随着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和危机。之后,这场衰退扩散到其他富裕国家。2008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不到5%,而到2009年底,失业率接近10%,直到2016年9月才恢复到5%的水平。直至今日,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特别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来说更是如此。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25岁以上大学毕业生就业人口增加1300万(约25%),与此同时,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就业只增加270万,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口的就业仅增加5.5万。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就业增长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大衰退影响。 [5] 尽管经济复苏使最不熟练工人的工资有所增长,但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2008—2016年,绝望的死亡人数迅速上升,心脏病死亡率下降的趋势也发生逆转,而在此期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口的收入和就业情况极差,远逊于若经济泡沫没有破裂其应达到的水平。
面对金融危机,美国的政策反应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与欧洲相比还算成功。欧洲国家在这场经济衰退中的表现各不相同。一些国家没有受到影响,另一些国家则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削减了国家开支和福利,这要么出于它们自己的主动选择,要么由于自身的债务状况和欧元区成员身份使它们别无选择。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拟环境,我们可以在其中比较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会对国民健康造成什么影响。
正如本章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认为贫困或经济大衰退是导致绝望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我们不是要否认贫困会带来严重后果,也不想否认与贫困如影随形的痛苦和糟糕的健康状况,我们承认美国部分地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预期寿命也很低,并对此深感痛惜。这些比欧洲更糟糕的状况直接证明了美国的社会保障网及其医疗制度的不足。但是,简单以美国例外的贫困状况或经济大衰退解释绝望的死亡现象,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
在第十一章,我们将讲述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本章,我们想首先探讨可能误入的歧途。这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人们被问及什么可能导致绝望的死亡,他们通常的回答是贫困、不平等、金融危机,或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它们中没有一个是绝望的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因为太多人持有前面的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在解释的过程中,将贫困、不平等和金融危机纳入我们的论述。
从死者的死亡证明上,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关于他们的信息,包括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关他们教育程度的信息。但是,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了解的信息无从得知,包括他们的职业、收入、财富状况,以及他们是否身陷贫困。由于不了解这些信息,我们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到绝望的死亡是否与贫困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迂回地进行研究。
在绝望的死亡流行病暴发期间,全国的贫困率并没有出现同步上升的现象。官方贫困人口数字所统计的,是收入低于贫困线家庭内的家庭成员总数。20世纪90年代,当绝望的死亡流行病刚刚开始蔓延时,官方统计的贫困人口数字仍在稳步下降,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总人口的11%。随后,贫困率缓慢攀升,在经济大衰退前夕增至总人口的13%,在大衰退期间更是急剧上升,但在衰退后又开始缓慢下降。到2017年,美国的贫困率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种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绝望的死亡人数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完全不同。当然,官方的贫困人口统计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特别是这些统计没有考虑税收或福利,如所得税抵免或食品券,现在称为“补助营养援助计划”。尽管根据这些因素对调整统计数字非常重要,特别是这有助于评估福利制度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可以如何帮助人们,但任何调整都无法令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和绝望的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相匹配。换言之,长期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根本无法解释当前绝望的死亡人数的激增。
这一流行病在种族中蔓延的模式也很难与贫困人口的分布相对应。1990—2017年,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成年人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不到黑人的一半。 [6] 然而,至少到2013年,非洲裔美国人几乎没有受这一流行病荼毒。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经济大衰退开始,中年白人贫困率大致保持在7%的水平(在低于学士学位人口中,贫困率为9%),而白人中绝望的死亡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从更普遍的角度说,在一系列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中,黑人的表现都比白人差, [7] 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3年,几乎只是在白人中出现了大量绝望的死亡。无论影响了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是什么独特的因素,一定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群体更穷。
的确,美国长期存在严重的贫困现象,特别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口中。事实上,由于美国漫长而可耻的种族歧视历史,导致南方难以有效地实施贫困救济,因为南方各州的政府长期以来都由白人把持,而实际或潜在接受救济的对象则是黑人。多年持续的严重贫困会导致糟糕的健康状况,而种族主义和低水平的医疗保障、教育甚至卫生设施,则使情况更为严重。
然而,贫困并不是绝望的死亡人数激增的根源。因为时间对不上,死亡人口也太“白”,而且地理位置也对不上。图10-1显示了2017年各州25~64岁白人人口中(按年龄调整的)意外(或意图未定)药物过量使用死亡率,以及各州的白人贫困率。
当然,阿巴拉契亚地区,尤其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既是药物过量使用死亡集中的地区,也是贫困率较高的地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贫困率与药物过量使用死亡率的关联度并不高。在经济贫困程度不算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从佛罗里达州一路北上到马里兰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药物过量使用的死亡也很普遍。还有一些州,比如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虽然贫困程度很高,但因药物过量使用而死亡的人相对较少。 [8] 与此同时,自杀现象在落基山脉各州更为普遍,而那里的贫困程度并不是特别高。1999—2017年,美国山区各州的自杀率上升幅度更大,尽管那里的自杀率本来已经是美国相对比较高的。美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摆脱自杀的阴影。2000—2017年,美国2/3的州中年白人自杀率上升了至少50%。此外,酒精性肝病的死亡率与全国贫困率呈正相关。但在贫困率特别高的州(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阿肯色州),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并不是最高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州的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完全不喝酒。酒精相关的死亡率在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和佛罗里达州特别高,在西部各州(怀俄明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和南部各州上升得特别快。不管推动这一流行病蔓延的是哪种绝望,它显然与各州的收入贫困状况关联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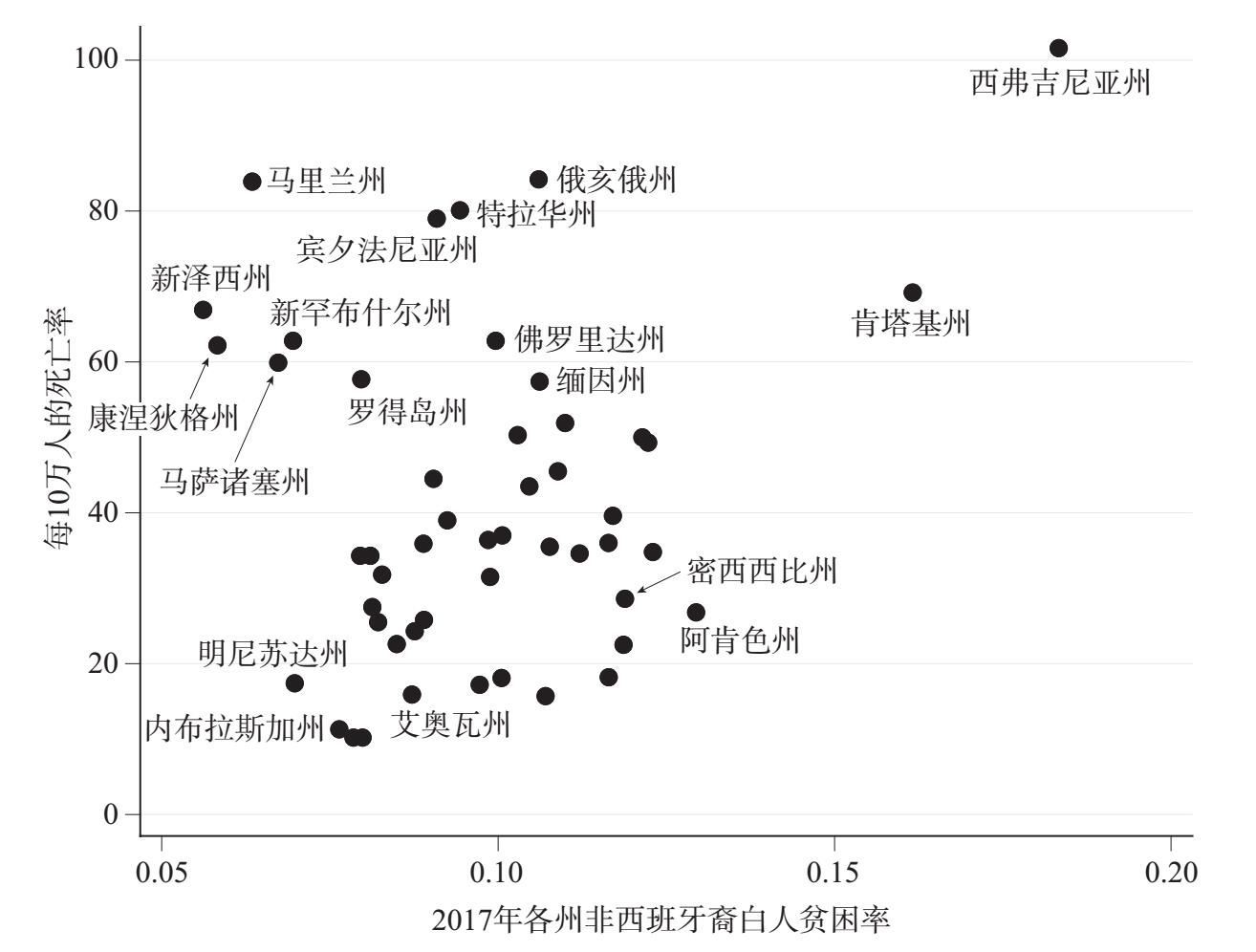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当年3月的当期人口调查结果
绝望的死亡在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人中非常普遍,这些人的生活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美好。收入在其中占据一定位置,尽管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收入下降与消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不过,劳工阶层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尤其是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精英阶层摘取,其他人一无所获。收入差距扩大正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绝望的死亡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平等本身就是导致社会混乱,包括死亡发生的罪魁祸首。我们认为,不平等之所以对人有害,是因为它破坏了社会和谐与人际关系,而这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曾提出,健康社会拥有的关系“是由促进社会团结的低压力联盟型战略所构成的”,而不健康的社会则充斥着“更具压力性的支配、冲突和屈服战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类型“主要取决于社会的平等和不平等程度” [9] 。这种观点与认为贫困是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的根源不同。后者认为,穷人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他们穷。与此相对,如果不平等会使一个社会总体上不健康,那么其中每个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而无论其贫穷还是富有。
威尔金森的理论有很多值得推崇之处,特别是它对社会环境而非个体环境的关注。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是否有助于解释当今美国的死亡率问题,以及不平等是否的确与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相关。我们一致认为,自1970年以来,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确实与绝望的死亡人数增加有关,但这种关联并不是直接的,可以简单地表述成“不平等让所有人都生了病”,而是因为在美国,富人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自己敛财,即劫贫济富。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收入不均状况加剧,死亡率仍在稳步下降,但最终,在1990年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绝望的死亡数量增加。我们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因为1%最上层的精英日益富有,而是因为白人劳工阶层自身发生的一切。当然,顶层精英日益富有与底层人士的困境可能存在很大关系,在我们思考应该做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时,这将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之所以陷入绝望,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社区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因为最顶尖的1%人口变得更富裕了。
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包括不同的城市和州),收入不均程度也有所不同。过去,收入不均程度较高的州死亡率较高,同时预期寿命也较短。今天,这两者的联系已经弱化。历史上,南方死亡率较高的各州,包括西弗吉尼亚州、亚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其收入不均的程度也高于其他大多数州。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因为这些州生活着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相对贫困,因而推高了整体收入不均的情况,而且他们的死亡率也相对较高,因而推高了总体死亡率。中部平原地区和西部大部分地区各州的人口分布更为平均,死亡率也较低。然而,时至今日,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经济收入特别不平等的两个州。它们的族裔结构也高度多元化,拥有大量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但它们位居美国死亡率最低的州之列。
因此,如果希望证明收入不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简单且直接的联系,无疑踏上了另一条歧途。
许多人认为,如果人们能较容易地摆脱贫困状态并实现富裕,或者至少下一代能够比父母生活得更好,那么收入不均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例如,某人的父母在收入分配中位居垫底的20%,但他自己却设法进入了收入的前20%,这个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假设,当代际流动性很高时,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也可能失败)。当代际流动性很低的时候,人们被困在他们出身的阶层。经济学家拉吉·切蒂与合作者计算了1980—1991年出生在美国不同地区的儿童的代际流动性。 [10] 他们的研究显示,出生在美国东南部的儿童向上流动的机会最小,至少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这样。虽然低流动性和绝望的死亡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但二者间的联系并不比不平等与绝望的死亡的联系更紧密。事实上,不平等本身与低流动性之间就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1929年10月,股市大崩盘,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0年的苦难和经济萧条。这段时期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数百万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工作、储蓄、家园或农场。超过20%的人口失业,这不仅使他们自己,也令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1929—1933年,美国人均收入减少了25%,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在美国 [11] 和英国 [12] ,自杀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来也再未被超越的高峰。在欧洲,大萧条及其后发生的一切则催生了法西斯。
自此以后,再未出现过比那时更糟糕的局面,但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仅次于此,虽然尚未到大萧条的地步,但是已经陷入经济大衰退。失业率翻了一番,从5%增加到10%,虽然这个数字没有20%那么糟糕,但对于数百万受到影响的人口而言,这也绝非幸事(对于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失业率最高仅达到5.3%)。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房地产泡沫,银行家大量发放本不该发放的抵押贷款,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数百万人因无力偿还贷款而失去家园。努力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突然丢掉工作,失去安居之所,也失去继续支持自己或子女接受教育的资金。银行停止放贷,数百万小企业破产。
已有许多研究专门探讨了死亡率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的变化,看是否有更多的人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死亡,就像我们起初可能预计的那样,还是更多的人死于经济繁荣时期,即所谓的好日子。有关这个问题的首个研究成果可能早在1922年就已发表,它是由社会家学兼统计学家威廉·奥本以及社会学家兼人口统计学家多萝西·托马斯共同发表的。 [13] 托马斯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位女教授。奥本和托马斯吃惊地发现,经济表现良好的时期恰恰是死亡率高企的时期。他们的结论在此后被验证了很多次,包括在大萧条前针对美国全国和州一级商业周期进行的研究。 [14] 其他富裕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经济衰退期反而比繁荣时期更有利于降低死亡率,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证实这一模式。诚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自杀率会更高,就像在大萧条时期一样——我们肯定都记得1929年破产的前百万富翁从摩天大楼一跃而下的画面——不过,还有其他机制也在起作用。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手头没有余钱做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事情,比如开快车或喝太多的酒,同时工作减少也可以减轻压力和降低心脏病发作的概率,此外,在工资较低、劳动力充足的时候,找到合适的人手照顾老人也会更便宜。 [15]
然而,每一次经济繁荣和衰退都各不相同,有自己的特点。在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经济上的灾难就伴随着死亡的流行病,后者正是本书的主题。那么,这次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重要的起点是回顾第四章的内容,尤其是图4-2,它揭示了1990年后绝望的死亡率轨迹。图中的上升轨迹几乎势不可当,没有迹象表明2008年的危机及其后的长期衰退对轨迹产生了任何影响。危机之后,自杀率自然非常高,但在此之前自杀率已经上升很多年。不管这次危机到底带来什么后果,没有证据显示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或者失业率在2008年秋季到2009年翻了一番之后,绝望的死亡人数激增。显然,如果认定经济崩溃导致了绝望的死亡,依然是误入歧途。
即便如此,经济大衰退也可能与其他类型或与某些群体的死亡人数增加有关,而与其他群体的死亡人数无关。例如,45~54岁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升,但在2000年后开始下降。 [16] 他们的全因死亡率(其中包括绝望的死亡,但不仅限于此)在1990—1999年持续下降,然后掉头上升,直到2016年,这一死亡率的趋势与他们的收入趋势呈反向相关,似乎符合人们的预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关联有其偶然性。这种全因死亡率下降和上升的趋势,是因为绝望的死亡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并且在开始时数量很小,因而被心脏病死亡率的降低抵消。
图10-2显示了上述时期45~54岁白人的绝望的死亡(药物、酒精和自杀)人数和心脏病死亡人数,以及这两种类型的死亡人数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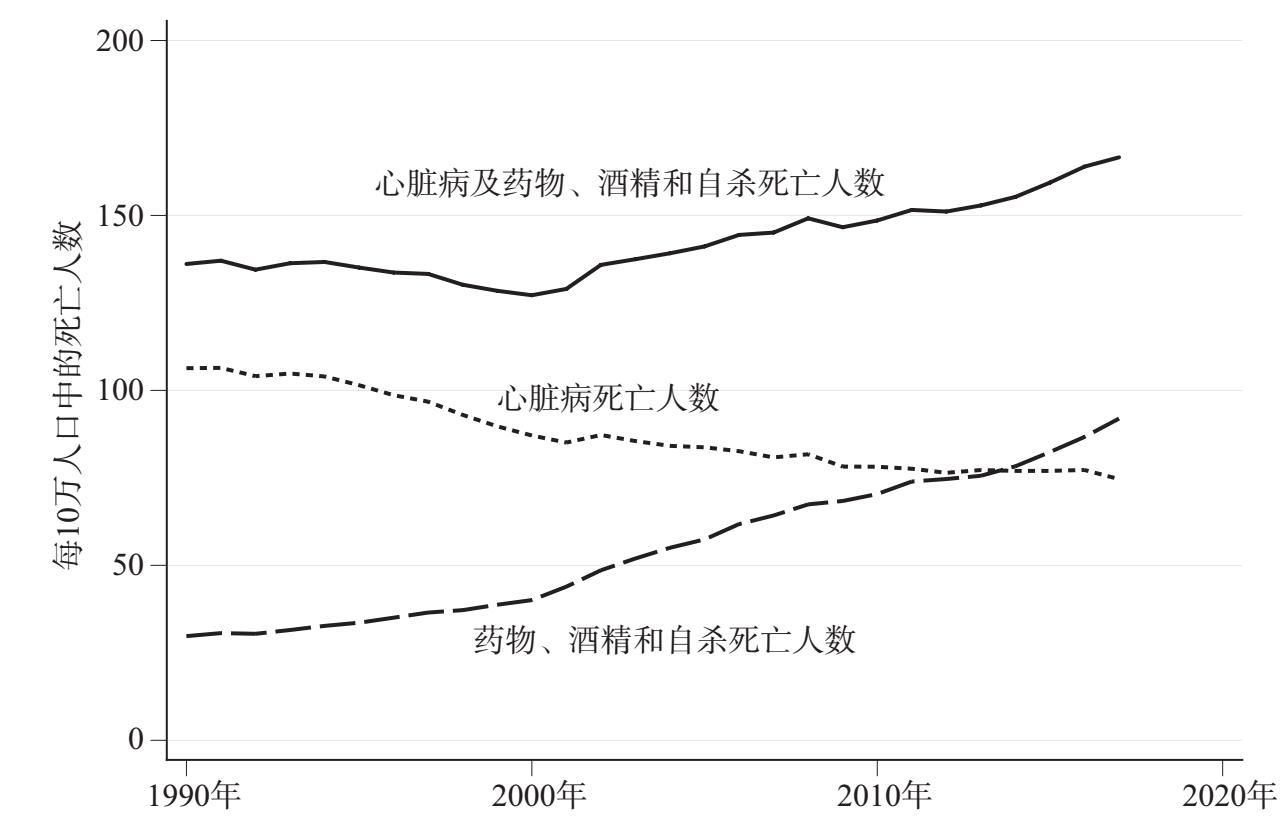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随着心脏病死亡人数的下降趋势放缓,以及绝望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一定水平,全因死亡人数也随之由降转升。不过,绝望的死亡和心脏病死亡这两大全因死亡的关键组成部分都与收入情况无关,而二者叠加后的趋势与收入趋势呈现相关关系只是巧合而已。
随着收入中位数的增长,老年白人的死亡率在这期间都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对老年人收入的保障优于对中年人收入的保障,因为退休人口的社会保障福利比尚在工作人口的工资中位数表现更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能看到收入趋势的上升和死亡率趋势的下降,如果因此就把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归因于他们的收入增加无疑过于草率。
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出,1990—2017年的收入变化模式与死亡模式并不匹配。例如,45—54岁的白人,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收入高于那些受过某种形式大学教育但未获得学位的人,而后者的收入又比那些只拥有高中或以下文凭的人高,这三类人群的家庭人均收入依次递减,并且在2000年前全部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在2000年后则全部开始下降。但这三个群体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则各不相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死亡率持续上升,中间组群体的死亡率持平,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死亡率则不断下降。如果比较黑人和白人人口,收入变化与死亡率的关联同样不存在,这两大群体也都经历了收入中位数的上升和下降,但死亡率走势却截然不同。其中,黑人的死亡率表现良好,白人的则很糟糕。正如贫困不能用来解释不同地区的死亡率表现一样,1990年后的收入变化模式也无法解释同期内死亡率的变化模式。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证明收入(或工资)无关紧要。在本书的其余章节中,我们认为绝望的死亡应归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在长期内机会不断减少。这里最有效的表达是“长期”。我们之所以怀疑经济大衰退对死亡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短短的20年间,死亡率的变化和收入的变化之间缺乏联系。
经济大衰退对美国和欧洲的打击并不一样。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无论以失业率上升,还是以收入下降幅度衡量,其遭受的打击都比美国大很多。对于那些实施紧缩政策的国家,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尽管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政府依然削减了失业救济金,并减少了卫生支出,尤其是在预防性服务(如疫苗接种和乳腺癌筛查)和药物领域。政府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如养老金和长期护理,则基本未变。受打击最大的希腊将公共卫生支出削减30%,但也没有削减需长期护理老年人的支出。 [17]
在欧洲,无论是在实行了紧缩政策的国家,还是在那些没有实行紧缩政策的国家,都未曾(现在也没有)发生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美国死亡率先降后升的走势在欧洲也没有出现。事实上,2007—2013年,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均增长了两倍多,有超过25%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但在此期间,这两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增长反而比欧洲多数国家还快。在此期间,欧洲各国的预期寿命开始趋同。一些原来预期寿命较短的国家,如爱沙尼亚、波兰和捷克,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高于那些预期寿命本来就比较长的国家,如挪威、法国和瑞士。但希腊和西班牙的情况并不能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两个国家原来的预期寿命就已经相当长,并且都在经济紧缩时期,死亡率也有了显著提高。 [18] 因此,审视欧洲的情况也对我们构建有关失业、收入下降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毫无帮助。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正在追随美国的脚步,并面临劳工阶层家庭收入持续恶化,身陷绝望的死亡的风险呢?英国似乎正处于山雨欲来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低收入工作家庭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加。1980—2011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每年增长超过2.4个月,但在此后陷入停滞。与美国一样,中年人心脏病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也已停滞不前,英格兰和苏格兰绝望的死亡人数都开始上升,其中苏格兰的情况尤为明显(与美国当前的数字相比,英国的数字仍然相当小,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局面刚开始恶化之时,绝望的死亡人数同样不多)。英国目前正处于紧缩政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的时期,伦敦地区蓬勃发展,但其他大部分地区则发展乏力。像美国一样,英国在政治上也处于分化状态,一半英国人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另一半人投票支持留在欧盟。截至2019年中期,尚不清楚这种情况对其死亡率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但自1970年以来,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生活水平长期下降的阴影很有可能正悄悄地笼罩英国上空,同时绝望的死亡人数也已开始抬头。 [19] 但是,对于英国最近的死亡率趋势,目前也尚无清晰和公认的解释。 [20]
我们关于收入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有些关于这一流行病的文章,如萨姆·奎诺内斯的杰出著作《梦之地》,生动地描绘了阿片类药物和死亡如何在曾经繁荣的城镇中肆虐泛滥,这些城镇中的工厂要么在竞争中败给了自动化,要么迁往国外,因而已经没有工作可寻,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则通过滥用阿片类药物麻醉自己。
如果把绝望的死亡与就业率准确地进行关联,例如,我们此前所做的那样,将美国划分为1000个小区块,则可以有力地证实奎诺内斯所看到的情况。在那些长年人口就业率低下的地区,绝望的死亡率也很高。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致死的单独数字。有些研究还关注一个更为具体的事件,即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于突然面临中国廉价商品的竞争而导致的失业率急剧增加。同样,失业率的上升也与死亡率的上升密切相关。 [21]
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绝望的死亡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阶层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较长时期内缓慢地遭到破坏。失业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那些放弃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士并未被计入失业人口,但他们仍然使就业人口的比例下降。失业率时升时降,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然是正常现象,但在特定的地方会出现某些工作被另一些工作取代的现象,而且往往是由比较差的工作取代比较好的工作。在一些制造业衰退、高薪工作消失不见的地方,失去这些工作的人可以找到其他工作,不过这些工作往往是在服务业,或者订单执行、呼叫中心的工作,甚至是优步网约车司机。这些工作可能报酬较低、工作压力更大,但它们至少能使人们留在劳动大军之中。
记者艾米·戈德斯坦讲述了保罗·瑞安的家乡——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市的故事。因时薪极高而被称为“慷慨”汽车公司的通用汽车公司曾在简斯维尔生产雪佛兰汽车长达83年,但其在2008年关闭了在那里的工厂。最后,虽然那里的失业率只有4%,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 [22]
较低的失业率确实与较低的绝望的死亡率相关。然而,可能有些人虽然失业并退出了劳动大军,但并没有被计入失业统计数据。他们无疑会对总体压力和绝望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当失业率看上去很低,但许多人无所事事并且无事可做时,死亡率依然高企。
总之,失业率并不总是确定一个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否遭到破坏的指标。糟糕的工作仍然算是一份工作,当人们完全放弃、停止寻找工作时,他们将不再被算作失业人口。但是,这些变化在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后,必将摧毁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带来了绝望的死亡。死亡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联系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就像所谓的“中国冲击”一样。对我们的故事来说,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们只是一部电影的最新一幕而已。
我们已经强调过,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美国和英国引发了自杀流行病,经济大衰退并没有带来绝望的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我们有理由怀疑,右翼民粹主义的高涨和左翼反对不平等的愤怒都与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还可以相信,精英们做事值得信赖,首席执行官和银行家对高薪受之无愧,因为他们服务了公共利益,因为经济增长和繁荣可以弥补金融体系的缺陷。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普通人损失惨重,甚至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住房,而银行家们却继续拿着高薪,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并继续受到政客的庇护。资本主义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劫贫济富的骗局,而非推动整体繁荣的引擎。
[1] Raj Chetty, Michael Stepner, Sarah Abraham, et al., 201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15(16), 1750–66.
[2] Irma Elo and Samuel H. Preston, 1996,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United States, 1979–85,”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42(1), 47–57.
[3] Kathryn Edin and H. Luke Shaefer, 2015, $2.00 a day: Living on almost nothing in Ameri ca , Houghton Mifflin; Matthew Desmond, 2016,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 Crown;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2017, “Statement on visit to the USA, by Professor Philip Alston, United Nations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15, https://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 NewsID=22533; Angus Deaton, 2018, “The US can no longer hide from its deep poverty problem,”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4.作为全球贫困人口统计的官方出口,世界银行根据全球贫困标准,估计美国有53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但最近使用行政数据进行的研究认为,世界银行(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用于计算贫困的调查低估了美国贫困人口从社会安全网中获得的福利金额,参见Bruce D. Meyer, Derek Wu, Victoria R. Mooers, and Carla Medalia, 2019, “The use and misuse of income data and extreme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25907,May.几乎可以肯定,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这种比较的真实性仍然无法解决。埃丁、谢弗、戴斯蒙德和奥斯顿(较小规模)的民族志研究记录了美国存在的贫困怪象。
[4]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2009,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 ties stronger, Bloomsbury. See also the wide range of claims at the Equality Trust’s website, https://www.equalitytrust.org.uk/.
[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5, “Table A-4: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25 years and over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 Retrieval: Labor Force Statistics (CPS), https://www.bls.gov/webapps/legacy/cpsatab4.htm.
[6] Census Bureau, n.d., “Poverty,” accessed September 19, 2019, https://www .census .gov /topics /income - poverty/ poverty. html;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3月当期人口调查。
[7]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3月当期人口调查。
[8] https://overdosemappingtool.norc.org/提供了一个用于药物过量和贫困的出色的交互式图表绘制工具。
[9] Richard Wilkinson, 2000, Mind the gap: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health and inequality , Dar-winism Today, Orion, 4.
[10]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2014,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29(4), 1553–623.
[11] David M. Cutler, Edward L. Glaeser, and Karen E. Norberg, 2001, “Explaining the rise in youth suicide,” in Jonathan Gruber, ed., Risky behav ior among youths: An economic analysis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9–79; Julie A. Phillips, 2014, “A changing epidemiology of suicide? The influence of birth cohorts on suicid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114, 151–60.
[12] Kyla Thomas and David Gunnell, 2010, “Suicid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61–2007: A time trends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39, 1464–75.
[13] William F. Ogburn and Dorothy S. Thomas, 1922, “The influence of the business cycle on certain social condi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8(139), 324–40.
[14] Christopher J. Ruhm, 2000, “Are recessions good for your heal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5(2), 617–50.
[15] Ann H. Stevens, Douglas L. Miller, Marianne Page, and Mateusz Filipski, 2015,“The best of times, the worst of times: Understanding pro- cyclical morta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 7(4), 279–311.
[16] 如需了解从种族和教育的角度对收入和死亡率之间关系进行的更全面分析,参见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2017,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 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 Spring。
[17] Ben Franklin, Dean Hochlaf, and George Holley- Moore, 2017, Public health in Europe during the austerity years,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 /public-health-in-europe-during-the-austerity-years.
[18] 关于欧洲的人口预期寿命,还有另一个刚刚显现的谜团。在2010年之后的几年中,最健康国家的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一直在放缓,2014—2015年,至少有12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下降。尽管这种想法颇具吸引力,但这并不能说明欧洲大陆正在追赶美国,并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在欧洲,预期寿命的下降是由于老年人口死亡率上升,而在美国,预期寿命的下降是由于中年人口或更年轻人口的死亡率上升。在欧洲,2015年初几个月的流感季节情况非常糟糕,疫苗对病毒不太有效,造成许多老年人死亡。作为某种补偿,2016年初几个月的死亡人数比平常少,因为许多体弱多病的人已经“被收割”(是的,这是人口统计学家的标准术语),并且2016年的预期寿命相对于2015年出现了反弹。英国是一个例外,预期寿命并没有反弹,同时有关紧缩政策及其影响的激烈辩论因为死亡率的情况而更趋激化。西蒙·雷恩–李维斯对此留下了一份精彩的记录(2017年,“Austerity and mortality”),参见其博客“Austerity and mortality,” Mainly macro (blog), November 25, https://mainlymacro. blogspot. com/2017/11/austerity-and-mortality.html。
[19] Rob Joyce and Xiaowei Xu, 2019, Inequa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troducing the IFS Deaton Review ,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May, https://www.ifs.org.uk/inequality/wpcontent /uploads/2019/05/The-IFS-Deaton-Review-launch.pdf.
[20]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8,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in mortality in England ,December,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 _data/file/762623/Recent_trends_in_mortality_in_England.pdf;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18, “Changing trends in mortalit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2000 to 2016,” August 7,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 birthsdeathsandmarriages /lifeexpectancies/articles/changingtrendsinmortalityaninternatio nalcomparison/2000to2016; Jessica Y. Ho and Arun S. Hendi, 2018, “Recent trends in life expectancy across high income coun-tries: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BMJ , 362,k2562, https://doi.org/10.1136/bmj.k2562.
[21] David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en, 2018, “When work disappears:Manufacturing decline and the falling marriage market- value of young men,” NBER Working Paper 23173, revised January; Justin R. Pierce and Peter K. Schott, 2016,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U.S. counties,” NBER Working Paper 22849,November.
[22] Amy Goldstein, 2017, 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 , Simon and Schuster.
教育差距,尤其是横亘在是否拥有学士学位人口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地使人们的生活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生活得不错,而另一部分人则生活得很艰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死于药物、自杀和酒精的人数空前增加,但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全部来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描述的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疼痛)恶化的加剧也是如此。
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来说,健康状况只是在他们的厄运清单中排在最前面的项目。他们在收入、工资、工作参与度、能找到的工作类型以及获得成功的机会等方面,与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的差距都正在扩大。人口的地域分布也越来越受教育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迁居到遍地成功和创新机会的城市,在那里能够找到好工作、好学校和好的娱乐活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则只能困守在农村、小镇或停滞不前、了无生气的社区中,出身于此但最有才华的下一代也早已纷纷逃离这个环境。60年前,迈克尔·杨曾预测,精英制度将导致这种分化,在本书第五章,我们也曾论述这种分化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中出现。
工作收入为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支持,因为这些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但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工作使生活井井有条,并赋予其意义。工作带来社会地位,而这并不等同于收入。工作收入还能够支持人们结婚生子。在此方面,上述两个群体也存在日益扩大的分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离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婚外生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子女分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对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更详尽的论述。
认为幸福等同于金钱,或者幸福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人们关心和在意的许多东西并不能够简化为钱,或者简单地用金钱衡量。不过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缺乏金钱,那么获得其他那些东西也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物质财富减少确实是生活痛苦的一个重要来源。被进步的经济抛弃是本书所述之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但这只是开始。在我们使用“绝望的死亡”一词时,“绝望”所代指的远比物质匮乏更为广泛,也更为严重。
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探讨物质财富的基础,即工作和工资,以及它们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中日益扩大的差距。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讨论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美国还呈现出另一种分化现象,不过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而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分化。其时间分水岭是1970年左右,尽管不同事件的具体时间略有不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0年,经济增长较快,经济成果分配相对均衡。经济增长好像一部自动扶梯,带动所有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共同进步。但在1970年以后,这部自动扶梯一分为二,一部扶梯的乘客是受过良好教育、已经相对富裕的人口,它的运行速度比以前更快;而另一部扶梯的乘客则是没有学士学位、本身就不太富有的人口,这部扶梯被卡住了,几乎一动不动。1970年以前,经济稳步增长,不平等现象没有加剧。在此之后,经济增长率下降,不平等现象则有所加剧。我们在后面将继续讨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部分原因,但毋庸讳言,它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劳工阶层的生活慢慢陷入困境。
在第十章,我们已经讨论过,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虽然是灾难性的,但它并不是导致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的根源,绝望的死亡流行病在更早之前就已发端,并在经济大衰退中愈演愈烈。事实上,最早开始于1970年的生活水平长期演变与这一流行病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此期间,白人劳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其所在的社会开始解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贴切地将其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二者都是缓慢但不可逆转地发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人们的注意。例如,气候变化的结果并不会反映在每年的气温波动中,但是其长期影响(对这一点人们仍然存在争议)威胁着人类文明。同样,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劳工阶层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越来越落后,而经济成果则越来越多地留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
总体经济状况会为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设定大的框架。人均GDP的增长可能会被用在许多地方,如支持政府支出、个人支出或企业设备支出,其中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也可能流向富人、穷人或平均地流向每一个人。查看总体经济增长只是分析问题的第一步,还需要将其分解,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从中受益。在20世纪50年代,人均经济年增长率为2.5%,10年后的60年代,达到3.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增长率最高的10年。1960年,人均GDP比1950年增长了28%。到1970年,这个数字比1960年增长了36%,比1950年增长了75%。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均经济年增长率下降到2.2%,而在90年代这个今天被认为经济增长还不错的10年,人均经济年增长率略低于2.0%。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经历了经济大衰退,经济总体年增长率不足1.0%,即使步入第二个10年,至少到2018年,在经济逐步复苏期间,经济年增长率也不到1.5%。更重要的是,美国并不是富裕经济体中唯一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个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目前有37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富裕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成员的经济增长率普遍出现了同样的下滑趋势。
在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资源的分配,即决定哪些人应得到什么资源,变得更加困难。 [1] 即使经济增长率出现微小差异,但如果这种现象长期持续,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经济年增长率为2.5%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水平在28年内(仅仅过了一代人)即可翻番。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为1.5%,则这一过程需要47年。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分配问题并不那么突出,即使某个群体得到的份额超过它应得的公平份额,也总还会有一些剩余给其他群体。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不太成功的群体完全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较低的增长加剧了对资源的争夺,促使每个团体都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游说,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大份额的利益,它还会毒害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资源分配有关。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红利主要流向了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这些人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应得利益。当人们觉得他们必须在一个更艰难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经济地位时,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分配的零和博弈,而远离创新和增长的正和博弈。寻租将取代创造,而我们将陷入一个使每个人都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
今天,关于收入不均的事实已经广为人知,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中下层的人口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极少,而那些处在中上层的人口,尤其是那些在最上层的人(前1%的社会名流),确实获益良多。低增长,再加上分配不公,对于中下层人口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双重打击。
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分化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富裕国家。不过,尽管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相似,但收入不均现象的加剧程度却并不相同。一些富裕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收入不均的程度直到最近才略有增加。此外还应看到,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从一开始就比这些国家严重得多。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富裕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近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尽管确实是多数富裕国家的共同趋势,但其最早出现在美国,并且美国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另一个分析经济增长和分配的角度是看国民收入中有多少被分配给劳动(工资),有多少被分配给资本(利润)。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工资与利润之比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常数,大约是2∶1。但这一情况自1970年以来也发生了变化,工资的比例从67%下降到60%左右。其他富裕国家,以及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 [2] 当然,并非所有的利润都流向富人(别忘了那些持有股票来补充退休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但利润的主要流入对象无疑还是富人,而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利润倾斜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现象加剧的原因之一。劳动在收入分配份额中的减少意味着,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不再等比例地带来工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不仅生产率的增长放缓,而且工资增长的步伐甚至落后于本已放缓的经济增长。在1979年以前,工人报酬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但从1979年到2018年,生产率增长了70%,时薪仅增长了12%。 [3]
国民收入是衡量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收入如何在国民中进行分配。为此,我们需要关注个人或家庭。我们论述的一个核心元素是,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收入存在差异,特别是在拥有或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之间,收入的差异更为明显。考虑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在健康和其他方面的差异,我们在此更感兴趣的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差异,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不均。
我们再次强调,收入影响的重要性可能不如社会变化,如工作性质、地位、婚姻和社交生活的改变。所有这些社会和经济变化正在同时发生,并共同作用,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它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我们会对此努力进行解读。人们普遍认为,劳动所得收入是导致其他后果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其加以检视。
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的收入比没有学位的人高。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从收入方面看,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口与仅有高中文凭的人口,其收入的差距在1980—2000年翻了一番,即在此期间收入差距从原来的40%飙升至80%。 [4] 教育会带来经济回报,这是因为人们在大学里学到了知识,还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与生俱来的更大动力或更强的认知能力,也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家庭关系,或者上述三者的综合作用。对于大学教育的溢价翻番的一个主流解释是,教育和认知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日益重要,因为生产越来越依赖复杂的技术,并从农业向计算机转移,从肌肉向大脑转移。这一过程被称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大学教育溢价提升同样也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不过,与整体不平等的情况一样,美国的溢价水平和增长速度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但美国是最极端的例子,其他英语国家紧随其后,但不像美国那样极端。在此方面,美国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夸张,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看到类似的情况。
学士学位的收入溢价是对接受教育的奖励,也是对上大学的激励,它对热衷于物质回报的年轻人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上大学是一个好主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好处越来越大。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这种现象似乎无关痛痒,只是一个指标,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发挥作用,将资源吸引到最需要的地方,并创造出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然而,这些激励措施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1996—2007年,取得学士学位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此之后虽然出现增长,但增长幅度也较为有限。2008年,在25岁年龄组中,有27%的人拥有学士学位,到2017年,这一比例仅上升到33%。 [5]
更糟糕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是因为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收入增加,还因为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收入减少。换言之,一方面,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被给予更高的收入作为奖励,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努力上大学的人还受到了收入降低的惩罚。赢家得到了奖品,输家的境遇则比什么都没得到还要糟糕。
图11-1追踪了不同出生队列人口的时薪(简称工资),显示了白人男性的工资变化走势。每一条线显示了一个特定出生队列在其工作年限内的工资中位数(经通胀调整);横轴显示了年龄,这使我们可以追踪每个出生队列随着年龄增长的工资变化情况。为了使数据清晰可读,我们只展示了4个出生队列的结果,他们分别出生于1940—1944年、1955—1959年、1975—1979年和1990—1994年,我们将每个队列进一步划分为拥有学士学位的群体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图11-1中的线条经平滑处理,以方便读者查阅。
图11-1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人口间的工资差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所有出生队列(顶部)的工资曲线都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底部)。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队列,到50年代出生的队列,再到70年代出生的队列,工资曲线不断上升。至于90年代出生的队列,因为他们还太年轻,所以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工资曲线走势如何。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从较早出生的队列到后期出生的队列,工资曲线则呈现梯次下降的走势。箭头方向指明了这两个不同人群一生收入模式的相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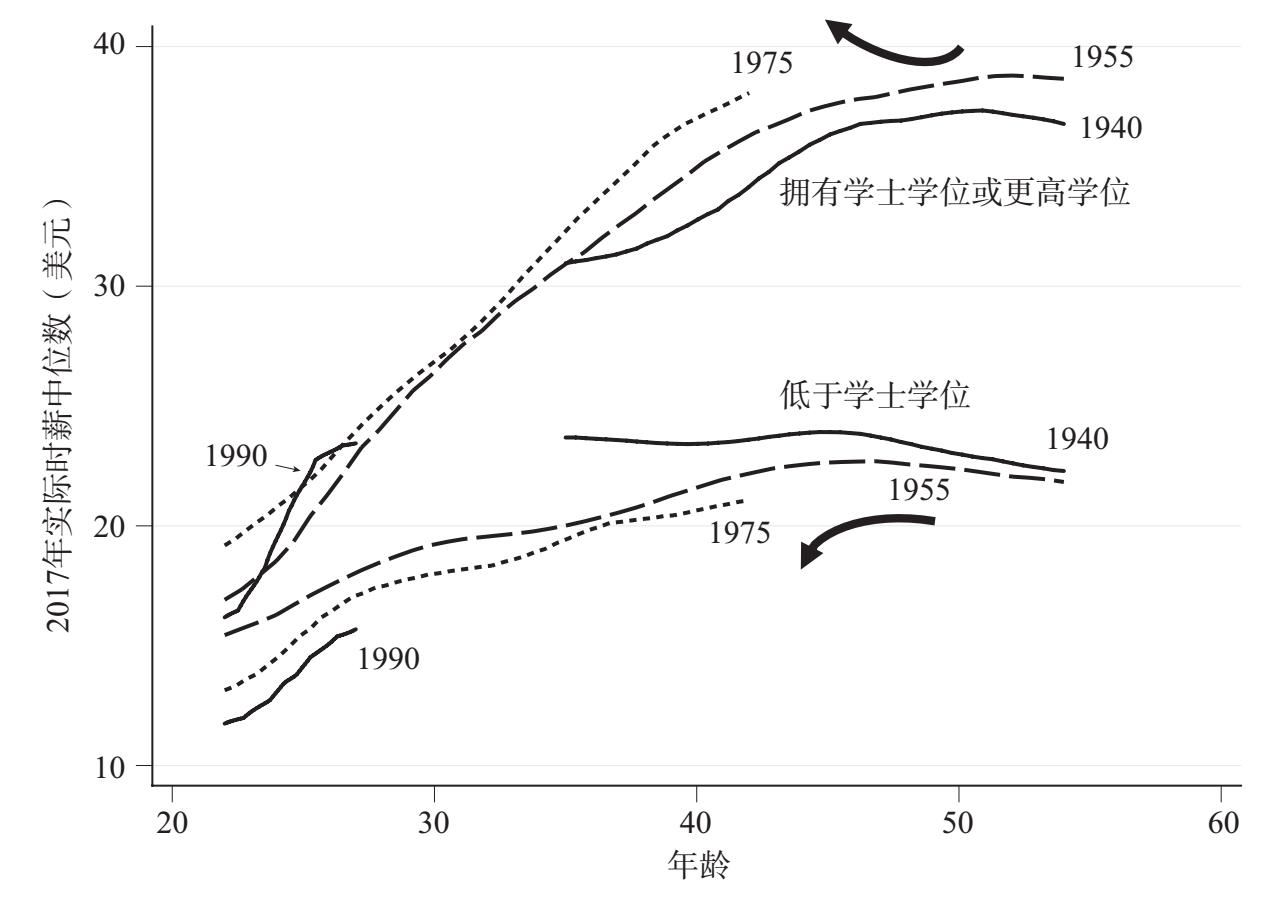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结果
这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在刚毕业的时候,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的收入只略高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男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1955年出生的男性22岁时(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全职就业者),有学位男性的工资中位数只比没有学位的男性高7%。到他们54岁时,学士学位的收入溢价已经增长到77%。每个出生队列的工资都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后者随年龄增长工资也大幅增加的可能性很小。在1955年出生的队列中,当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工资中位数达到最高值(45岁时),他们的工资比自己在22岁时的工资增长了50%。而对于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他们的最高工资中位数(50岁时)比自己22岁时的工资高了2.5倍。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他们的收入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持续增加,而更多体力工作者的收入在中年时达到峰值,随后开始降低。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下降,在相同出生队列中,对于晚生人群来说,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每一代人的大学教育溢价都比上一代人高。
图11-1提供了很多信息,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在图下部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部分,从每个出生队列到下一个出生队列的工资几乎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较年轻的工作年龄段更是如此。相反,在图上部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部分,每个出生队列到下一个出生队列的工资基本上都在持续增长。显然,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目前在获得工作回报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
与图11-1中男性的情况一样,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在时薪方面同样呈现了随出生队列梯次增长的趋势。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女性来说,1940—1950年的出生队列,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20世纪中期之后出生的女性工资则没有实现增长。在1965年之后出生的人口中,没有学士学位的女性的平均工资与前一个队列相比,也呈现下降趋势。
如果将所有25 ~ 64岁的白人就业者加总并进行通胀调整,他们在1979—2017年的平均时薪总体增长了11%。这意味着年均增长率为0.4%,而在此期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5%。50年来,美国男性的工资中位数一直持平,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而言,其在1979—2017年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每年负0.2%。
工资中位数长期不变似乎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独有的现象。在欧洲,经济大衰退及其后果也导致工资增长乏力。许多国家遭受了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出现了双底型衰退。2007年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英国的平均工资都出现下降。但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美国就业者所经历的工资长期停滞现象。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参照。英国工人的工资也已开始下降,但在此前的20年里,当美国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动时,英国的实际工资中位数增长了近一半。因此,即使英国的工资开始下降,典型的英国工人的收入也比20年前高,而不像没有学士学位的典型美国工人那样,只能拿到比以前低的实际工资。 [6]
也许政府的数据不准确,或者被曲解了,工资的实际表现好于图11-1所示的情况。 [7] 如果工资的表现好于滞胀,那么也许美国资本主义事实上以统计数据无法捕捉到的方式为美国工人提供了支持。本书的论点是,美国劳工阶层的生活艰难是一个事实,虽然工资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它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首先想要强调的是一个老生常谈,那就是工资并不等同于物质福利,而物质福利本身则是一个比福利窄得多的概念。即使工资表现糟糕,人们仍然需要面对更多不得不花的钱。现在的女性与1970年相比,更有可能外出工作,因此,即使个人收入没有增加,家庭总收入的中位数也可能提高。事实上,家庭收入中位数的表现的确好于收入中位数。如果妇女是出于自主选择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在日益困难的环境中维持生计,那么增加妇女的就业参与是一桩好事,其意义甚至超过她们的收入。但是,如果夫妇中的一方为了更好地抚养孩子而本来宁愿不工作,但为了在经济上维系家庭而不得不工作,那么所有家庭成员的福利都可能受影响。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1978—1999年),美国妇女之所以更多地参与全职工作,实际上都是出于经济压力,而不是个人成就感” [8] 。尽管目前的双亲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父母双方都有全职工作,但59%的美国人(以及一半的职业母亲)认为,父母双方中如果能有一方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会更好。 [9] 孩子和通勤费用通常会消耗掉多出来的那一份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而我们在分析家庭收入时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此外,对工资的分析并没有考虑税收或福利因素,一些福利,如所得税抵免,提高了低收入劳动者的税后收入。工人还可以通过雇主获得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和政府福利,特别是医疗补助(医疗补助计划通常针对65岁以上的人口,他们不是本书主要的关注对象),他们也能够通过社会安全网获得福利,包括食品券和残疾保险。核算这些项目相当困难,特别是那些不以现金形式出现的项目,例如,医疗保险。雇主或国家为了提供这些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接受者所得到的价值并不相等,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把美国医疗保险过高的成本当作劳动人民获得的一种现金福利来计算。医疗行业通过游说、兼并或削弱竞争来抬高价格,或者剥夺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压低那些应由雇主提供保险的工人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是将收入从工人转移到医疗行业,如果把这算作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实在离谱,事实与此恰恰相反。由于医疗保险福利成本的增长大部分是因为价格上涨,将医疗福利费用加到家庭收入之中,几乎肯定会导致收入增长被高估,而不是相反,即忽略这些福利会导致收入增长被低估。同样,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费用增加也是导致收入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之一。
即使这些福利的价值可以按人们愿意支付的费用来衡量,它们也和现金福利不一样,除非因为拥有它们,人们可以自由地将那些本来需要购买这些福利的现金用作他途,否则它们并不能为人们提供等同于现金的自由。医疗补助金不能用于购买食物或交房租,而现金则可以让人们做那些用实物福利不能实现的事。因此,税后现金收入,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税后工资,仍然是衡量人们是否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关键指标。
工资和收入主要花在食品、住房、娱乐和医疗等方面,如果这些价格上涨,工资实际上会相应贬值。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依据人们所购商品的价格变化对货币工资加以修正,这一修正是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做出的,而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一篮子消费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变化。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夸大了物价逐年上涨的幅度,那么收入的长期增长情况就会比我们预计的要好,并且对两个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体来说,都会比图11-1所显示的结果更好。
消费者价格指数夸大物价上涨幅度的一种方式,是它可能并未充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商品和服务比过去更好,它们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也许医疗费用比过去更高,但它所提供的服务也比过去更好,诸如常规髋关节置换术、白内障手术、控制高血压的药物,还有无数其他的医疗奇迹,这些都是半个世纪前所没有的。诚然,确实有一些科技进步虽然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并未体现在收入增长或价格降低上。不过,与不做任何修正相比,对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修正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质量的提升是否能让人们在获得原有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时少花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从质量提升中受益。在某些情况下,它正是如此发挥作用的。设想有一种高质量的汽油,它可支持的行驶里程是原来的两倍,因此它的推出和原有汽油降价一半的效果完全一样。但大多数质量提升并非如此,原有的低质量产品通常会退出市场,因而人们没有选择,只能花钱购买质量提升后的产品或服务。你的车现在拥有安全气囊,因此是一辆质量更高的车,但实际上,你已经无法买到一辆没有安全气囊的车了。你可能很喜欢某种新产品,比如你的手机,但它通常不会让你的生活更便宜。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过去一直享有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如果65岁以上老年人的寿命延长,这无疑会增加老年人的福利,但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断言,因为老年人的福利比过去有所增加,所以他们的生活成本下降,而他们的养老金现在看起来太高了吗?这种说法,以及有关一个典型的工人的生活实际上比其收入表现更好的说法,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各方面生活质量的提升,包括医疗,也包括由于互联网而能够更好地享受娱乐,或者自动取款机带来的便利,能够让人们减少购买这些质量更高的产品的数量,或者减少购买其他产品,因而这种质量提升可以实实在在地转变成现金,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无论多么诱人,通常都并不存在。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些技术创新而更快乐,然而,尽管人们一直为金钱能否买到幸福而争论不休,但是我们无疑尚未找到一种方法,能够用幸福买到金钱。
在过去10年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表现不佳,而且按照报告就业的人口比例衡量,他们中还在工作的人也更少了。在处于正式工作年龄(25~54岁)的男性中,就业人口比例一直在持续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群体中只有5%的人口没有工作。到2010年经济大衰退结束之时,他们中高达20%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在2018年,当经济早已步入复苏后,仍有14%的人没有工作。在这14%的人中,只有20%的人声称处于失业并正在寻找工作的状态,其余的人已经彻底退出就业人口大军。
再一次,上述这一趋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中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图11-2给出了1980—2018年,25~54岁白人男性和女性中的就业人口比例,并按照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灰色)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黑色)加以区分。垂直线标志着经济衰退的年份,我们通常会预计在这些年份,因为工作数量减少,就业人数会下降。当经济复苏的好时光回来之后,许多失业的工人会重回工作岗位。但并不是每次经济衰退之后,所有适龄男性都能重新找到工作,所以虽然就业人口比例在每次衰退之后都会回升,但它们从未恢复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业人口比例逐渐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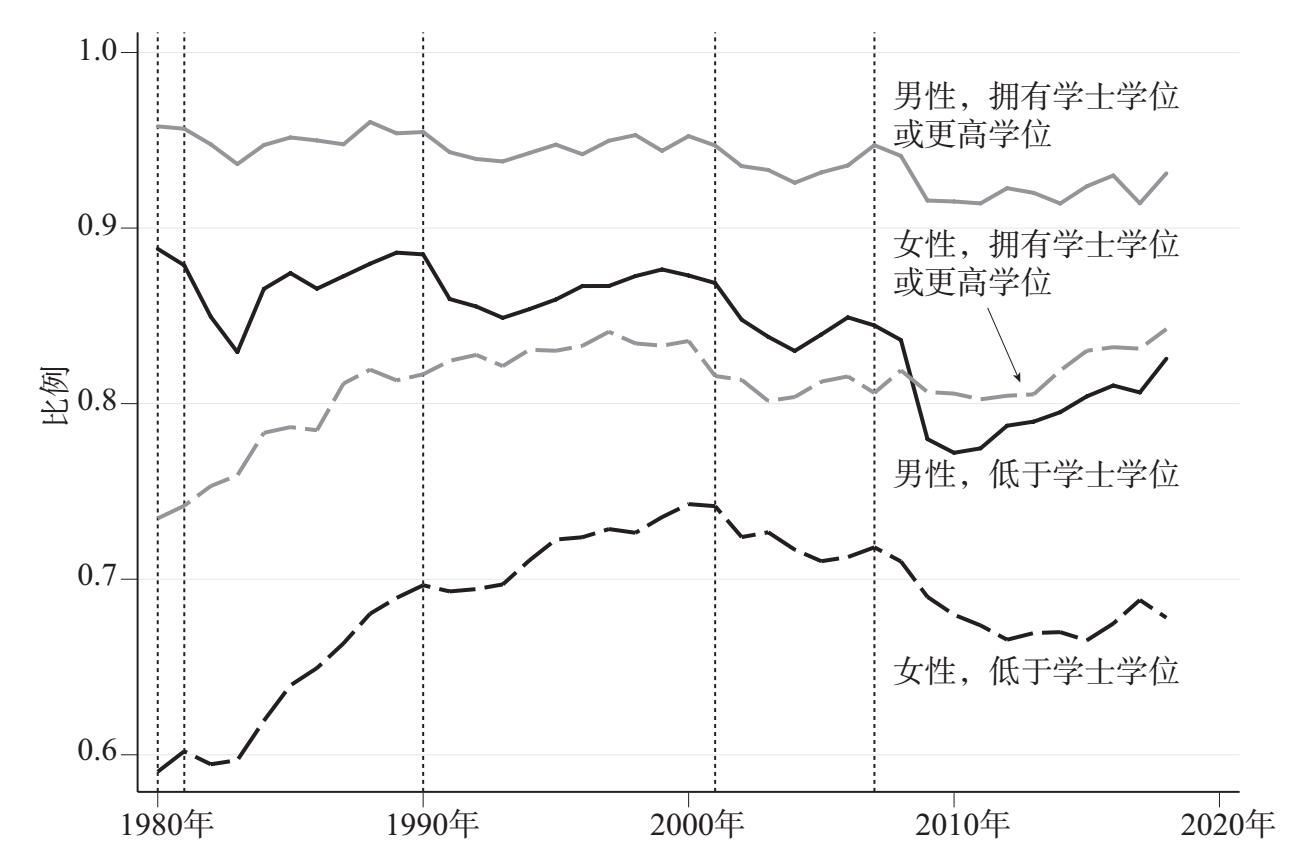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结果
2000年以后,就业比例下降的趋势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中更为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能够找到的好工作正在消失,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拥有学士学位和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就业率差距不断扩大。在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由于避孕药的问世和性别歧视的减少)。事实证明,女性就业比男性就业更能抵御经济衰退的影响。不过,在2000年之后,女性的就业率也有所下降——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人口就业率下降的幅度较小,而没有学士学位的女性人口就业率下降的幅度则比较大。这些各不相同的就业人口比例模式,导致目前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的就业人口比例已经高于没有学士学位的男性。
部分(也许高达一半)的就业率下降,可以由工资下降来解释 [10] ——在工资较低的时候,人们更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有部分下降可以由我们在前面已经写过的残疾人口增加来解释,这其中包括阿片类药物依赖的影响;另外部分下降则可以由现有工作的吸引力下降来解释。
自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工作已经不复存在,其中许多是高薪工作,例如,在通用汽车或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厂工作。在过去,劳工阶层男性跟随父辈,有时甚至是祖父辈的脚步,进入制造业,并从事高薪且有工会保护的工作,他们挣的钱足够支撑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住宅,送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并且能够定期休假。这些人被称为蓝领贵族。但现在,很多这样的工作都已消失不见。尽管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持续增长,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却迅速减少。自制造业岗位在1979年达到1950万的历史最高点后开始减少,到2007年经济大衰退前,美国制造业工厂的就业岗位减少了500多万,降至1380万。在金融危机期间,制造业岗位更是遭受巨大打击,又有200万个岗位消失不见,虽然在此之后,制造业岗位数量有所反弹,但这个行业已经不太可能重新获得经济大衰退期间失去的所有就业岗位。这些工作已经被国外进口的产品或工厂自动化、全球化和机器人取代。
这一切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而言都不是好消息。有些人放弃寻找新工作。大多数人设法找到其他工作,但这些新工作通常工资较低,或者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较低。这些新工作的自主性可能会降低,可供自由发挥或与他人互动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并且福利更低,工作保障也更少。例如,被归为临时工的工人不能享有意外险。从事这些新工作的工人可以被轻易替代,人员流动率高,而且雇主几乎不给他们任何承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只要人们一直干下去,他们的工资就不会越来越低,就算真有这种情况也极其罕见,因此,从一份好工作换成一份不那么好的工作才是导致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我们撰写这本书的时候(2019年),美国25~54岁男性的失业率为3%左右,所以对于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来说,工作岗位相当充足,只不过这些工作不再是以前的工作,特别是面向低学历男性的高薪制造业工作。这也是这么多人不再找工作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人们不愿工作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不工作。当然,做出选择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圣女贞德选择了火刑,但这只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更糟,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今天,那些选择不工作的人已经不再拥有从前那些选择,因此做出这种选择也许是无奈之举。尽管这么说并不能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他们只是变得更懒或更不愿意工作,或者因为看到可以依靠别人或国家生活,从而使他们选择游手好闲。
到底是因为丧失了勤奋精神,还是由于外部环境恶化,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我们在第五章讨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时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本章的数据显然指向了外部环境。图11-2显示,在经济衰退期间,大量工人离开就业市场,这导致图中明显的棘轮。人们突然爆发的懒惰与经济衰退不谋而合,这显然非常奇怪;相反,合理的预计是惰性会稳定增长。 [11] 显然,人们之所以离开就业市场,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存在,而随后大多数人都通过积极寻找工作,及时找到其他工作。将图11-1和图11-2综合起来看,会提供更多指向外部环境的证据。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来说,就业率下降的同时工资也在下降。如果人们变得不那么勤奋,并从劳动大军中抽身出来享受生活,那么工资水平应该会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工作的数量没有变,但愿意工作的人减少了。工资和就业量一起下降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证明雇主正在减少雇用员工的数量。
有些人选择不工作,可能是因为社会安全网使他们无须工作就能生活下去,特别是(尽管不仅仅是)残疾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正在越来越多为不工作的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然而,请回想一下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写到的疼痛症状大量增加与身心健康恶化的现象,残疾人口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普遍存在的健康不佳,而不是人们在钻福利制度的空子。 [12] 欧洲拥有比美国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包括对失业者的长期救济和慷慨的残疾福利制度,特别是针对老龄工作者。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包括以慷慨的福利制度而著称的丹麦、挪威和瑞典,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加入了就业大军。一种逻辑认为,上述国家针对诸如儿童保育等服务提供了一系列补贴,从而使人们更容易出去工作。 [13] 而另一种逻辑是,美国人与别国人不同,只有美国人对福利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福利也能让他们放弃工作。但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4]
在人们选择不再工作时,工人的供给量会减少,那么工资就不会像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替代工作时那样下降。无论是反对社会安全网的观点,还是支持必须满足一定的工作要求才可以使用社会安全网的观点,事实上都是在支持降低工资。如果能够强迫更多的人出去工作,图11-1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口的工资下降幅度会更大。其他一些提议也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包括工作应成为获得医疗或其他福利的先决条件,或者诸如所得税减免等计划,这些福利只有工作的人才能得到。它们都会把人们推向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降低其价格,也就是工资。
如果工作本身确实就是一件好事,那么较低的工资还能够被工作本身的好处弥补。人们希望得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和社会地位,他们在工作中学习,接触他人,并因而拥有更好的生活。一个相反的观点是,很多工作都是纯粹的苦差,休闲本身就是愉悦和自由感的提升,所以即使支持让他人来支付休闲费用,也不失为一件好事。那么按照这种观点,既然我们常常乐于为那些食不果腹或居无定所的人提供补贴,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对待休闲呢?正如伯特兰·罗素曾经指出的那样,最强烈主张穷人应该更多地工作的人,恰恰是那些从来没工作一天的闲散的富人。 [15] 这些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将在第十六章探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尤其是在备受争议的普遍基本收入问题上该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劳工阶层。19世纪,支持并定义劳工阶层生活方式的制造业工作开始出现,吸引工人逐步从农业岗位转向工厂的岗位。这一过程在内战后开始加速,在1950年左右达到顶峰。即使到1950年,家庭主妇仍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角色。在那之前,夫妇双方必须同心协力,合作谋生。现在,男人们去工厂工作,在那里,他们不需要拥有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教育水平,并且他们通过艰苦的生产劳动,而不仅仅是较高的工资,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16] 男性整日在外,为了养家而辛勤工作,而家务和孩子则交由配偶负责。这种生活方式还遵从着严格的社会规范,即男性要想结婚,首先应有确定的前途,婚外不能发生性关系,更不用说非婚生子了。制造业和随之而来的劳工阶层生活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以及其家庭生活应有的样子。 [17]
制造业的兴起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意义的新方式。大概在同一时期,加入工会的人数也达到顶峰。虽然并不能说工会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并且工会长期以来主张的一些福利现在已经成为对雇主的法定要求,但在工作场合中,从没有人像工会那样全力为工人争取利益。在分配利润时,工会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帮助工会会员的工资上涨(相应也使非会员的工资有所上涨,尽管幅度较小),他们还会监督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加入工会的工人不太可能辞职,而且往往更具生产力。 [18] 工会为工人带来了一些民主掌控力,不仅在工作中,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而且后者往往是当地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当美国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到顶峰时,约33%的劳动大军是工会会员。 [19] 2018年,工会会员的比例已经降至10.5%,其中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人数仅占员工总数的6.4%。 [20]
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消失,工人们不得不从事不那么理想和不那么正规的工作,主要是医疗、餐饮服务、保洁和保安等领域的服务性工作,而不再是制造业的工作。雇主对工人的承诺下降,员工的承诺也相应下降;工会与雇主之间的战争已被相互疏离的关系取代。 [21] 许多不太理想的服务性工作属于个人发展或产出增长潜力都很小的工作,或者工人必须随时随地严格遵照指令行事,毫无个人主动性地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实际上是机器人的临时替身,只是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工作,直到程序员教会机器人替代他们。 [22]
詹姆斯·布拉德沃斯描述了他在亚马逊公司于英国的一个仓库中的经历。他遇到一位名叫亚历克斯的人,对方告诉他:“人们现在会说‘我在亚马逊工作’,但过去,人们从来不会说‘我在矿井工作’,而是会说‘我是一名矿工’,因为工作意味着你是谁,并且你为此感到骄傲。” [23]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富裕国家,都有一些大公司专门提供外包工人,包括清洁工、保安、餐饮服务人员或司机,在过去,这些工人本来会直接受雇于接受外包服务的公司,并在那些岗位上赚取相对较高的工资,但现在,他们不再是其工作之地的雇员。他们的工资相对较低,通常没有福利或充分的员工保障。这种做法使得高科技公司,比如谷歌,可以只雇用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员工,其他支持性员工则来自另一家公司提供的外包服务。根据布拉德沃斯在英国的经历,以及美国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报道, [24] 在亚马逊仓库(被称作“配送中心”)工作的工人,只有很少的人是亚马逊的正式雇员。在美国的案例中,属于亚马逊正式雇员的少数员工和许多由诚信员工解决方案公司(Integrity Staffing Solutions)派驻的“临时工”之间唯一明显的区别,是他们的徽章颜色,一个为蓝色,一个为白色。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差别,相似的人做着相似的工作,但那些外包员工(有时是前雇员)的工作条件往往更差,工资更低,福利更少,升职的可能性有限或根本没有。
那些有才华的孩子,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无缘接受其能力可及的教育,就再也不能从一个看门人变成一位首席执行官,因为看门人和首席执行官根本不会属于同一家公司,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25] 当今世界已经分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后者不再有希望加入前者。或许最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外包员工不再是主体公司的一分子,他们不再对其拥有认同感,正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形象地指出, [26] 他们不再受邀参加节日派对,他们再也找不到作为一家大企业的一员(尽管是地位低微的一分子)而感到的骄傲、意义和希望。
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崩溃还有另一面。在很多地方、很多公司,过去都只有白人劳工阶层,非洲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外。与黑人相比,白人持续多年拥有特权。这种特权现在已经被削弱或消失不见,用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的话来说,“在一个蓝领劳动阶层的总体机会不断收缩的环境中,白人劳工阶层会认为,黑人的进步是对机会的不公平掠夺,而不是削弱其所处的种族特权地位。” [27] 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0%的美国白人劳工阶层认为,对白人的歧视问题与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问题一样严重,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白人中,则有70%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 [28]
人们在失去原有优越工作的同时,还失去了依托这些工作而存在的家庭生活,并且至少在认知层面又失去了种族特权,甚至会认为自己成了受歧视的一方。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其威力远远大于真实但可控的收入下降。
[1] Benjamin M. Friedman, 2005,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Vintage; Thomas B. Edsall, 2012, The age of austerity: How scarcity will remake American politics , Doubleday.
[2] 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2013,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29(1), 61–103.
[4] 1980年,女性的大学教育工资溢价高于男性(50%对30%)。2000年及以后,男性和女性的溢价水平都是80%。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
[5]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一些成年人直到年近30岁仍然在努力获得学士学位。2008年,在30岁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口比例为30%,到2017年升至36%。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6] Stephen Machin, 2015, “Real wage trends,”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Recession:From Micro to Macro Conference, Bank of England, September 23 and 24, https://www .ifs .org .uk /uploads/Presentations/Understanding%20the%20recession_230915/SMachin.pdf.
[7] White House, 2019,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 March, https://www. govinfo.gov /features/erp.
[8] Robert D. Putnam,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Simon and Schuster, 196–97.
[9] Nikki Graf, 2016, “Most Americans say that children are better off with a parent at home,”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10,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0/10/most -americans-say-children-are-better-off-with-a-parent-at-home/.
[10] Katharine G. Abraham and Melissa S. Kearny, 2019,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the US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io: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24333, re-vised August.
[11]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图11—2中看到棘轮效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青壮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呈显著线性下降趋势。男性退出就业市场的这场大逃亡几乎完全不受经济波动影响。”参见Eberstadt, 2018, “Men without work,” American Consequences , January30, http:// www.aei.org/publication/men-without-work-2/。
[12] 其他原因包括劳动力老龄化和调查包含的女性工人所占比例较高,因为妇女患病人数比男性多,参见Jeffrey B. Liebman, 2015,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 in disability insurance benefit receip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9(2), 123–50。
[13] Henrik Jacobsen Kleven, 2014, “How can Scandinavians tax so much?,” Journal of Eco nomic Perspectives , 28(4), 77–98.
[14] Lane Kenworthy, 2019, 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Bertrand Russell, 1935, 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 , Routledge.
[16] Michele Lamont, 2000, The dignity of the working ma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Andrew Cherlin, 2014, 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 class family in Amer ica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8] Richard B. Freeman and James L. Medoff, 1984, What do unions do? , Basic Books.
[19] Henry S. Farber, Daniel Herbst, Ilyana Kuziemko, and Suresh Naidu, 2018,“Unions and inequality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NBER Working Paper 24587, May.
[20]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9, “Union members summary,” Economic News Release, January18, https:// 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htm.
[21] Cherlin, Labor’s love lost .
[22] Emily Guendelsberger, 2019, On the clock: What low- 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 , Little, Brown.
[23] James Bloodworth, 2018, 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wage Britain ,Atlantic Books, 57.
[24] Guendelsberger, On the clock .
[25] Neil Irwin, 2017, “To understand rising in equality, consider the janitors at two top companies, then and now,”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3.
[26] Nicholas Bloom, 2017, “Corporations in the age of inequality,” The Big Idea,Harvard Busi ness Review, https://hbr.org/cover-story/2017/03/corporations-in-the-age-ofinequality.
[27] Cherlin, Labor’s love lost , 172.
[28] Daniel Cox, Rachel Lienesch, and Robert P. Jones, 2017, “Beyond economics:Fears of cultural displacement pushe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to Trump,” PRRI/Atlantic Report, April 9, https://www.prri.org/research/white-working-class-attitudes-economytrade-immigration -election-donald-trump/.
由于市场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提供的好工作越来越少,人们不得不转向较差的工作,或者彻底失去工作,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状况,而且也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之间,存在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在婚姻、养育子女、宗教、社会活动和参与社区等方面。经济学家往往只关注人们的实际收入,以此衡量其经济状况。事实上,收入固然很重要,但这远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想了解四分五裂的生活如何逼迫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走上其他形式的绝望的死亡之路,我们就需要关注他们生活的更多方面。毋庸置疑,我们在本章中概述的大部分此类研究成果都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因为社会学家往往会采用比经济学家更广阔的视角审视生活。
纵观西方历史,如果一个男人希望与一个女人共同生活并养育子女,那么他必须“适婚”。也就是说,他至少可以养活自己的新娘,并且拥有良好的“前途”。从前,新郎在向新娘求婚之前,必须首先征得女方父亲的同意,而父亲的义务是检查新郎是否能够养活自己的女儿。这个习俗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现在通常是由这对夫妇自己检查他们的经济状况。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且需要被迫接受不断下降的工资,适婚男子的供给量随之下降,同步下降的还有婚姻的数量。 [1] 劳工阶层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每个家庭只有男性外出工作,其工资足以维持一个家庭所需,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来说,这种理想现在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正在破坏劳工阶层的婚姻。
在图12-1中,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结婚率已经发生戏剧性变化,该图以10年为尺度,描绘了1980—2018年间30 ~ 70岁成年人中报告目前处于婚姻状态的人口比例。 [2] 左图显示了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情况,右图显示了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情况。在1980年(以两个图中顶部的长虚线表示),任何特定年龄的白人,无论是否拥有学士学位,处于婚姻状态的人口比例都几乎相同。到1990年,在两个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所有年龄段的婚姻率都有所降低,其中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婚姻率下降幅度普遍更大。1990—2018年,与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相比,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婚姻率持续下降。在1980年,无论是否拥有学士学位,82%的白人在45岁时都处于婚姻状态。到1990年,不同教育程度的两个群体的婚姻率都降至75%。1990年以后,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维持了这一比例,但年届45岁、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婚姻率则持续下降,在2018年降至62%的低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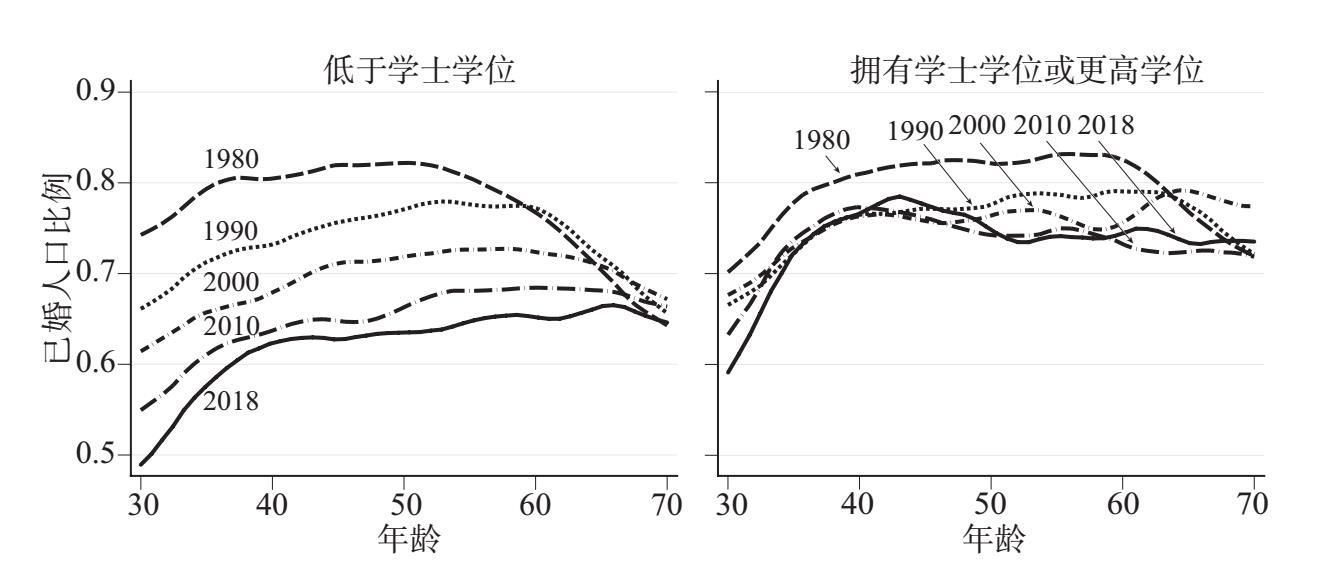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结果
婚姻有很多益处。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结婚,但对于那些希望结婚的人来说,婚姻带来了亲密感、伴侣感和满足感,对许多人来说,婚姻还带来了儿孙绕膝的快乐。已婚者寿命更长,更健康,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尤其是已婚男性,虽然说健康的人本来就更有可能结婚,但这一点并不足以导致这种差异。假设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因为适婚性下降而无法结婚,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问题不仅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恶化,还剥夺了婚姻带给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社会的全部好处。
对于那些不想结婚,以及那些在过去被迫结婚的人来说,结婚率下降是一件好事。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推迟结婚的年龄,以便接受更多教育、发展职业,或者仅仅是待价而沽,力求找到或至少努力寻找最理想的伴侣。对于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晚婚是他们30多岁时结婚率急剧上升的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避孕药得到广泛使用,同时1965—1975年的性解放运动使人们对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使男女间的非婚性行为在社会上被广泛接受,并且人们不必再担心意外怀孕。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使堕胎合法化,这可能也让人们对性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再那么担心。尤其是对许多女性来说,这些变化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降低了她们接受更好教育或进入职场的代价。由于有了避孕药,越来越多的妇女得以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3]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盛行的女权主义则鼓励妇女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自由。那些选择晚婚,甚至根本不结婚的人,牢牢抓住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更美满的人生。不过,接受大学教育似乎只会让人们推迟几年结婚,到35岁以后,75%的人已经结婚。
因此,造成人们不结婚的原因似乎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因为人们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因而错过了他们本想拥有的婚姻,另一类则是因为人们现在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因而主动选择暂时或永久退出婚姻。正如新的可能性(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出现后经常会导致的那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得失,那些更富裕或受过更好教育的人通常更加消息灵通,并有能力充分利用新的机会,成为最终获益的人。正如本书经常讨论的那样,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育程度的分化上。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人口的婚姻模式变化,与30年前黑人社区出现的变化如出一辙, [4] 而且其出现的主要诱因也基本相同。 [5] 因为没有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男人变得不再适婚,并导致稳定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变得遥不可及。
曾几何时,当婚姻和生育紧密相连时,婚姻数量下降意味着生育下降。事实上,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工资水平在控制生育率的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6] 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婚姻和生育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或者至少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就可以打破这种联系。现在人们有很多社会允许的途径享受亲密的性关系,同时安全、方便和可靠的避孕手段意味着,亲密的性关系不再带来怀孕的风险。人们在不放弃亲密伴侣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推迟结婚,也可以推迟生育,直到事业有成,或者有一个(相对)方便的窗口,可以暂停事业,生儿育女。与此同时,由于拥有方便的避孕措施,并且在需要时可以选择堕胎,男性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有时在女方家人猎枪的威胁下)出于尽义务而迎娶怀孕的伴侣。非婚性行为和非婚生育不再是社会的耻辱。 [7]
然而,所有这些解放都有黑暗的一面,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的。许多怀孕生子但并未结婚的妇女并没有和孩子的父亲同居,甚至不再与孩子的父亲保持联系,而是转而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并可能再生下对方的孩子。同居现象在其他富裕国家和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中同样有所增加。但是,带着孩子不断与不同男性同居,这种不稳定和脆弱的同居现象在其他国家极其罕见,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女性中也很少发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通常会推迟生育,直到她们完成学业并结婚。 [8] 按照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的说法, [9] 现在存在两种迈向成年的不同模式。一种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的模式,即先完成大学学业、找工作和发展职业,然后再结婚生子。另一种模式则适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包括连续同居和非婚生育。在美国,与多位伴侣生育孩子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
社会学文献适当地关注了这种生育模式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在破裂和脆弱的关系中的表现往往不如在完整的家庭中,因为完整的家庭拥有父母双方。事实上,连续同居和非婚生育对于成年人也会产生影响。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状态是绝望蔓延的主要原因。
人们可能会好奇,那些女性为什么要做出如此选择。男人不再受旧规则的约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女性在有了孩子后很可能面临经济困境、情绪不稳定和缺乏支持的恶性循环,有些人会觉得很难从中逃脱。但是,她们的选择可能十分有限。如果许多女性已经准备好在婚姻之外建立性关系,这就削弱了那些更愿意等待的人的议价能力。一旦怀孕,尽管许多妇女想堕胎,但也有许多人不想堕胎。堕胎现象并不罕见,不过堕胎数量正在迅速下降。按照2014年的数据,在美国,每四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在45岁之前堕过胎。同一年,在15~44岁的美国妇女中,每1000人中的堕胎数为14.6(活产数为62.9)。 [10] 对许多女性来说,生孩子被看作一种祝福,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一种救赎和未来的希望。对于那些无法想象自己能够上大学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成功。与宣布拿到一所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或者在工作中获得重要的晋升相比,宣布自己怀孕时的喜悦同样真实和充满希望。未来看起来如此光明而充满祝福,哪怕这种感觉只存在一瞬间。 [11]
对于单身妈妈来说,一旦有了孩子,将会通过“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获得福利支持,而这并不利于婚姻。这一福利对女性在怀孕后不急于结婚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在实施60年后,于1996年被取消的原因之一。
将父亲们也定义为这种现象的受害者似乎很难。毕竟,他们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获得了快乐,并且摆脱了一些经济和情感上的义务。但是,他们达成的是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开始看上去非常棒和充满前途,但最终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当他们人到中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事业和收入方面无法与父辈或他们对自己的期望相比,而且他们也没有稳定的家庭分享生活与回忆。他们可能在一系列关系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或全部)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陌生人,他们的一些孩子生活在其他男人的屋檐下。这种破碎而脆弱的关系很少能带来日常的快乐和舒适,也很少能保证中年男性过上幸福的日子。
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旧有的社会规则无论在当时多么限制自由和不可饶恕,它仍然饱含长期积累的社会智慧,因而可以阻止人们做出可能悔恨一生的决定。
我们此处描述的对象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但同样的论述早已被用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模式之上。我们在此再一次看到跨越种族的融合。自1990年以来,没有大学学历的黑人妇女非婚生育率一直维持在高位,但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并且在2010年以来开始稳步下降。相比之下,1990—2017年,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女性非婚生育率翻了一番有余,从20%上升到40%以上。随着黑人非婚生育率的下降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非婚生育率上升,阶级正在成为比种族更重要的鸿沟。切尔林指出:“如果你准备想象一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有多位亲密伴侣的典型女性形象,那么请想象一个只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女性。” [12]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描绘了20世纪最后30年社会资本显著下降的现象。 [13] 美国人越来越不愿参加与他人有关的社会活动,例如,家庭聚餐,晚上在家中招待朋友,以及教堂、工会和俱乐部等组织的活动。自帕特南的著作在2000年出版以来,这种下降趋势的势头未减,有些方面甚至还出现加速下降。与家庭模式一样,这种趋势也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中出现显著分化,并且其中一些方面的分化正在扩大。
物质生活水平、健康、家庭和子女是一个人幸福的基础,同样十分重要的还包括社区,以及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宗教信仰。2008—2012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 [14] 我们在此同样不需要遵循经济学家的做法,试图为这些生活的其他方面定价,或将其简化为货币等价物。我们无须勉强为健康、家庭、社区和宗教信仰套上衡量财富标准所必需的束缚,因为它们的重要性无法以其成本高低或人们愿意为之支付多少钱来衡量。
人们参与本地和全国性社区活动的一种方式是参政议政,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投票选出他们喜欢的候选人或政策。社区参与本身会带来直接回报,即使人们并不总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那些积极参与的人确实更有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65岁以上人口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比18~29岁年龄段的人口高出50%——在1996—2016年的历次选举中,有78%的老年选民投票,但只有53%的年轻选民投票——这与公共政策对老年人口相对更加慷慨有很大关系。收入与投票有关,教育也是如此,议员们更有可能为其选区内更富有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谋取福利。 [15]
图12-2按种族和教育程度分列了最近6次总统大选(1996—2016年)的选民投票率。每一个点都代表了25 ~ 64岁的选民在选举年份的投票率。1996—2008年(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投票率有所上升,此后则有所下降。从图12-2中可以看出,投票率最大的分化点是教育程度:不论种族如何,拥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投票率始终比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高出20个百分点。除了奥巴马参选的年份(当时非洲裔美国选民的投票率相对较高),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口中,白人和黑人的投票率没有显著差异。显然,投票率的分化也体现在不同的阶级,而非种族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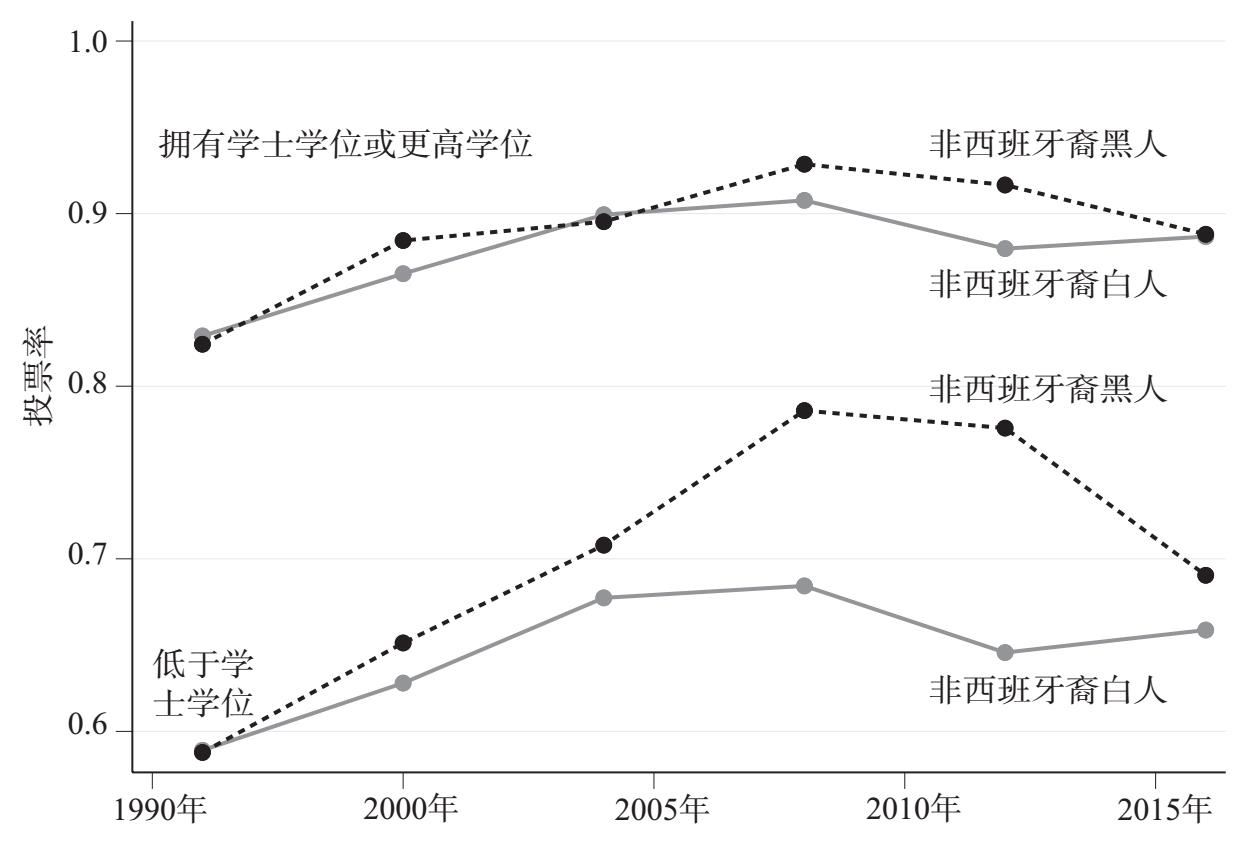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当期人口调查结果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工会会员人数迅速下降。对劳工阶层来说,工会会员显然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20世纪50年代中期,超过1/3的非农业雇员属于工会,但是从那以后,工会会员人数不断下降,到2017年已降至不到10%,其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人数基本相等。不过,考虑到私营部门雇用的人员数量远远高于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公共部门雇员加入工会的比例是私营部门雇员的5倍有余。私营部门工会的迅速退化是导致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力量不断增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工会退化也可能部分源于资本相对力量的这种变化),我们将在第十五章中再度讨论这个问题。与积极参政一样,加入工会不仅有助于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工会的会议和以工会为基础的俱乐部在许多地方还是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至少在过去是这样。
如果我加入了某个协会组织,这不仅对我个人有利,同时也会给其他人带来益处。因为我的加入,协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而这会给其他成员带来好处。我如果加入一个俱乐部或教会,也同样会起到类似的作用,这普遍适用于社会资本。我的加入带来了所谓的“网络外部性”,某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的成本和收益。这种情况体现在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在加入某个教会,归属感的好处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正如脸书的发展那样,人际网络的外部效应会导致会员数量快速增长,因为随着会员数量不断增加,其增长也会呈现加速的趋势。会员数量越多,新的增长就越快,至少直到没有更多的人对加入脸书感兴趣为止。反之亦然,当人们纷纷退出工会或教会时,其对剩下成员的吸引力也随之降低,正如加速扩张一样,具有人际网络外部效应的组织也可能迅速崩溃。这无疑在私营部门的工会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一旦人们开始离开,不仅工会大厅会被迫关门,工会运动队会解散,工会还会丧失为会员谋求福利的部分权力,而这将导致会员的归属感越来越低。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宗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大大超过除意大利(可能还包括爱尔兰)之外的其他许多富裕国家。信教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更好:他们更快乐、更慷慨,更有可能不吸烟、不喝酒或不滥用药物。拥有朋友会让美好的生活锦上添花,而同一教会的教友比其他朋友更能做到这一点。 [16]
近年来,美国的教会会员人数持续下降,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后者本来就较少去教堂。那些表示宗教对他们很重要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加入了某个教会或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今天,大约1/3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在此前一周去过某个礼拜场所。 [17]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定期去教堂的人口比例大概为50%,直到1980年,这一比例才开始缓慢下降,随后在2000年前一直稳定在40%左右,但在此之后,这个比例急剧下降。
我们常常认为,宗教是一个人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它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改变,至少如果这个人没有堕落。事实上,美国东北部的大量天主教徒是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留下的遗产,正如今天南部和西部天主教徒人数不断增加是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结果。宗教信仰不仅仅是移民史的活化石,它还反映了人们归属感的变迁,有时是脱离了陪伴自己成长的教会,有时是转投另一个教会门下,因为原有教会的教导似乎已不再有用,或不再符合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个有关性的社会规范和公民权利出现巨变、对政府的不信任急剧增加的时期,许多人完全不再去教堂,而其他人则对变化感到不安,对主流教会缺乏有力的回应感到不满,因而转向福音派和社会保守派教会。 [18] 2000年后,不但主流教会的教徒不断减少,福音派教会的教徒也不断减少,特别是那些没有像父母那样被这些教会信奉的社会保守政治信仰吸引的年轻人。许多美国人似乎是根据他们的政治信仰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
近年来,自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0年,只有7%或8%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到2016年,几乎25%的人口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年轻的劳工阶层白人(18~29岁)中,这一比例增加到近50%。 [19] 顺便说一句,这是美国人总体宗教信仰,以及美国社会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今天,只有4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白人基督徒,而在1996年,这一比例为65%,在2006年底,这一比例为54%。在美国,白人基督徒占人口多数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对白人劳工阶层中的部分人来说,这可能又将被视作一个不受欢迎的改变。
福音派和主流派教会的区别不仅仅只在于政治信仰。许多主流教会提供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思诺所说的“居所之灵性” [20] 。这些教会正是世世代代美国人的庇护所和礼拜场所,往往可以回溯到他们移民前的母国,例如,来自意大利、爱尔兰或墨西哥的天主教徒和移民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或者德国的路德派教徒。当经济或家庭生活面临挑战时,教会为教徒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当然,也有人认为教会愚化和压迫教徒。根据伍思诺的理论,与“居所”相对应的是“寻求”,即人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例如,转向适合自己社会保守主义思想的福音派教会,或者在既定教会之外创建自己独特的信仰融合体。这是个人主义盛行的表现之一,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所说,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21] 。这些替代之选可以为自由地探索灵性提供更大的空间,使人们除了某些人眼中压迫式的教会组织之外,还拥有更多选择,但它们可能无法提供主流教会具备的安慰感或毫无疑虑的接纳感,因为主流教会的仪式和传统人们从小就很熟悉,它们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可以提供帮助,并且在此前几代人也正是这样做的。许多美国人目前和任何有组织的宗教都没有联系,但他们通过自我建构,有时用孤立的信仰探索自身的灵性。在社会民族学家凯瑟琳·爱丁与合作者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有一位以“远古外星人造访地球”理论为中心构建其灵性的男性,他抱怨很难找到人来讨论这种信仰。 [22] 这种孤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了爱丁及合著者所称的“劳工阶层男性的脆弱依恋”。
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人们去教堂做礼拜的频率,图12-3显示了中年白人人口(40~59岁)报告自己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比例。由于样本数量很小,我们使用了20年的年龄范围,并对每年的波动做了平滑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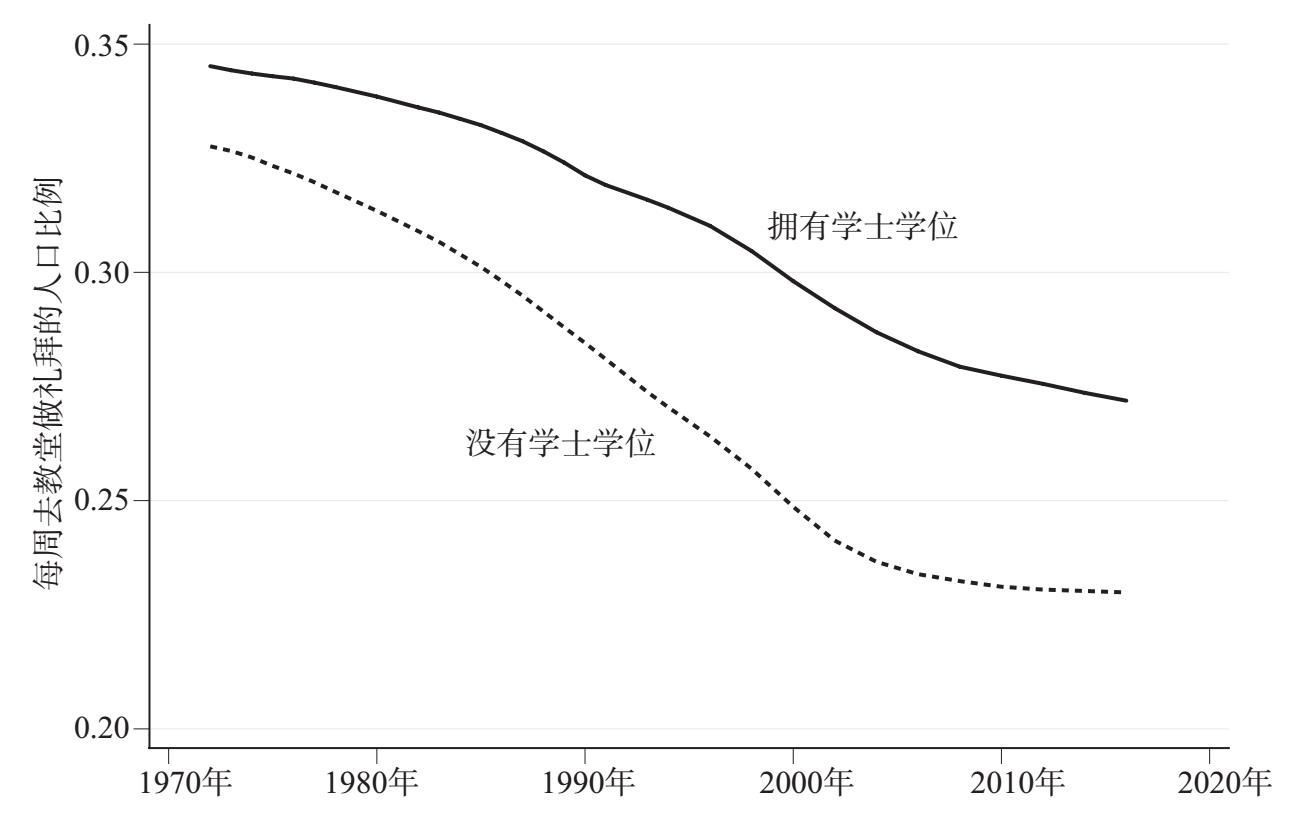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结果
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占更大的比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即使在年龄较大的人口中(他们通常比年轻人更不愿意退出教会),去教堂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下降的速度更快。显然,白人劳工阶层正在失去来自工会和教会的社区支持。
如果我们画出非洲裔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的比例(在此同样需要对较小的样本量提出警告),我们将发现,没有证据显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每周去教堂的比例有所下降。大约1/3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黑人会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这一比例与20世纪70年代初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比例大致相同,但黑人与白人不同的是,他们中定期去教堂的人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
为什么宗教信仰的缺失和教会的衰落会成为一个问题?美国受绝望的死亡影响最严重的州——西弗吉尼亚州,同时也是美国对宗教最虔诚的州之一——70%处于工作年龄的白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受绝望的死亡影响较小的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只有51%的人认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也许,如果西弗吉尼亚人不那么虔诚并不是一件坏事?
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宗教信仰会对社会和经济环境做出反应。全球,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贫穷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但在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西欧,人们的宗教信仰较低。有一种观点提出了一种世俗化的假设,即随着教育普及、收入增加,以及随着国家接管教会的许多职能,人们会远离宗教。简而言之,人们在较恶劣的环境中更需要宗教。这符合美国各州的情况,那些收入较低、来自州政府的支持较少的州拥有教徒的比例较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实上,虽然信教的人往往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信教的人做得更好——他们更快乐,更不可能犯罪,更不可能滥用药物和酒精,也更不可能吸烟——但是,那些拥有更多教徒的地区,包括美国各州,在上述方面的总体表现反而更糟糕。 [23] 虽然宗教能够帮助人们做得更好,但人们信奉宗教有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恶劣。当人们的宗教信仰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消退,他们将失去宗教所给予的支持,不得不独自面对恶劣的环境。
人们总是忍不住想要找到一个能够全面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期望它能够以某种方式综合考量所有对人们重要的东西,包括物质福利、健康、家庭、社区和宗教。我们认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如果勉强把生活的不同方面加诸一个单一指标,会让太多东西缺失,并且这样做并不比分别考量各个方面收获更多。近年来,一些作家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我们问人们他们有多幸福,或他们的生活如何,我们会得到一个神奇的数字,可以代替其他任何方面的指标。 [24] 许多优秀的哲学理论和经验论据都已经证明这一主张的错误性。即便如此,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依然很有价值,前提是我们不要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人们的自我评价捕捉的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收入、预期寿命或去教堂做礼拜的频率等“专业”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充其量只能算某种指标,而与衡量主体的感受无关。除此之外,有证据显示,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自我报告式生活评估指标会随着生活环境(包括收入、健康、宗教和教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于个人而言,自认为活得不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即使这并不能反映他们关心的所有方面。同样,当我们试图了解人们的生活质量时,我们可以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补充其他衡量标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使用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情况。在这个调查中,受调对象会被问及他们在“目前这段时间内的总体幸福感如何”,并要在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即非常幸福、相当幸福和不太幸福。图12-4显示了1972—2016年,年龄在40~59岁的不同群体回答这个问题时,报告自己“不太幸福”的比例。对于全体中年白人而言(用虚线表示),这个指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显示出变化,此后报告“不太幸福”的中年白人的比例开始上升。这种变化是由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推动的,通过分列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期间,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一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报告自己不幸福,但表达不满的人口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似乎一直比较稳定。在此之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人口中,对自己生活状态不满的比例开始增加,同时拥有学士学位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群体的差距也在稳步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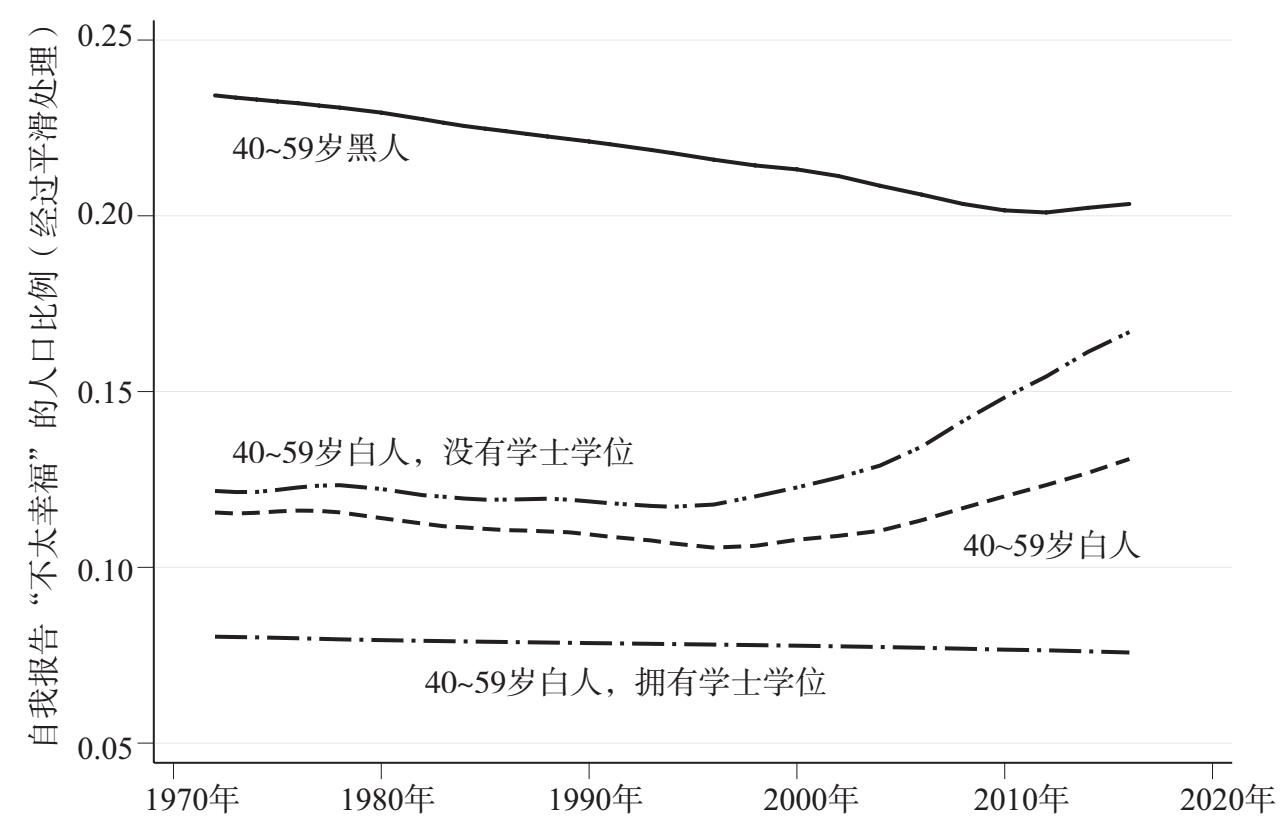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结果
与中年白人相比,更多中年非洲裔美国人报告自己不太幸福。不过,他们报告“不太幸福”的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稳步下降,之后稳定在20%左右(由于调查的样本量太小,无法按是否拥有大学学历进一步划分黑人人口)。如果这反映了真实情况——我们在此希望重申我们的警告,即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是否准确有待证实——那么幸福指数反映了一些在物质幸福指标数据中没有显示出来的东西,即非洲裔美国人虽然比白人更不幸福,但他们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改善,而对白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来说,情况则并非如此。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对生活状况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即坎特里尔阶梯,这种方法要求人们想象自己站在一个10级阶梯之上,每级阶梯用0~10标记,其中0是个人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生活,而10是最好的生活。这个方法有时被称为“生活阶梯法”。请注意,这个方法中并没有提到“幸福”二字,它只是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的生活。自2008年以来,盖洛普已经用这种方法对数百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我们有足够的数据详细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按照种族、年龄和教育程度进行分类研究。
图12-5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学士学位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间存在巨大差异,但黑人人口(以实线表示)和白人人口(以虚线表示)之间则没有巨大差异。事实上,40岁以后,没有学士学位的黑人对其生活的自我评价甚至优于学历相当的白人,而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中,年轻白人对生活的自我评价明显优于年轻黑人。无论黑人是否拥有学士学位,他们在人到中年后,其对生活的自我评价都不会像白人那样出现下降。为了避免我们的结论被误读,我们希望再次强调,自我评价并不是衡量所有人们觉得重要之事的最佳标准,并且虽然相同受教育程度的黑人和白人对生活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但这也不足以说明,我们可以忽视那些显示黑人生活状况更差的指标,或忽视拥有学士学位的黑人数量远远低于白人这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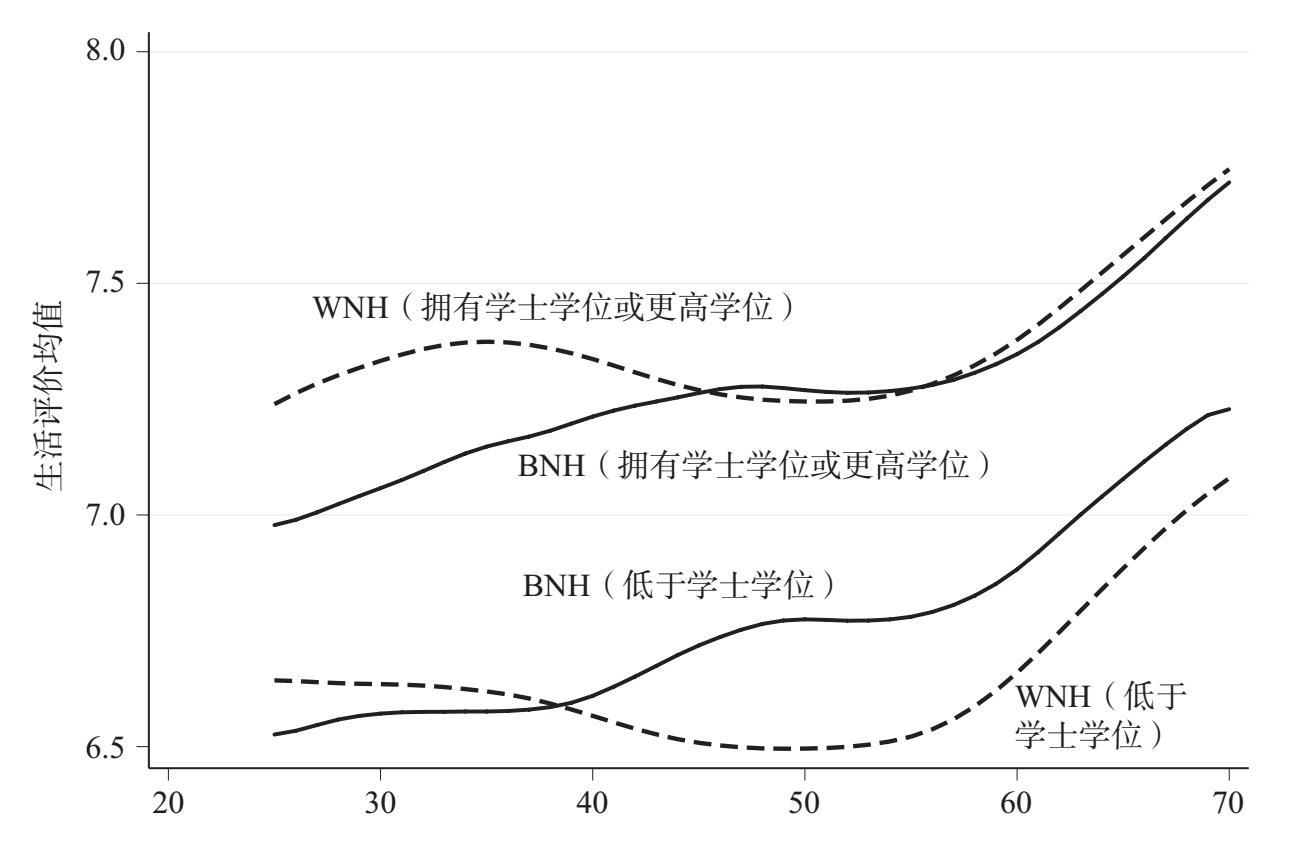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2017年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
盖洛普的调查问题中还包括人们是否正在经历压力或身体疼痛,以及他们是感到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指标中的大部分与“生活阶梯”指标一样,在不同受教育程度,而非不同种族的人口中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还普遍存在于体现人们日常乐观情绪的总体指标中,包括每天微笑、享受生活、感到快乐和痛苦的平均水平。 [25] 人们在这些体验中的不同感受完全是由其受教育程度决定的,而不存在种族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水平没有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在此方面的表现更好,他们中很少有人报告说,在调查的前一天经历了很大的压力。总体而言,在这些有关体验的衡量标准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受教育程度,而不是种族,这其中的例外只存在于压力水平,在这一点上黑人比白人做得更好。
生活远不仅仅是金钱,在本章中,我们研究了一些非金钱方面的因素,包括家庭、养育子女、宗教、参与政治以及生活评价自我报告。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而言,除了工资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持续下降之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远逊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同时在几个方面,尤其是婚姻和生育方面,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大。工会的衰落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人口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日趋恶化,他们也越来越与能够起支持作用的宗教和社区生活脱钩。我们很难相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能够弥补这些损失。
当然,归根结底,我们是在努力寻找一个解释,以回答我们在一开始时提出的可怕的死亡趋势问题,即绝望的死亡。工资下降显然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但我们认为,这种绝望不可能单纯通过物质福利的下降来解释。我们认为,家庭、社区和宗教的衰落是导致绝望产生的更重要原因。显然,如果传统劳工阶层生活所依赖的高工资和优越工作没有消失,这些衰落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认为,问题的核心是一种生活方式遭到彻底摧毁,而不是物质福利的下降。工资只是通过这些因素间接发挥了作用,但它不是直接的导火索。
非洲裔美国人在某些方面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结果非常发人深省。尽管近年来黑人工资增长幅度乏善可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增长,同时尽管黑人在大多数指标上的绝对表现远逊于白人,甚至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差,但黑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在改善,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的生活却在恶化。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对此加以审视,无疑将能更好地理解黑人与白人死亡率的变化趋势问题。
[1] An early statement is in David T. Ellwood and Christopher Jencks, 2004, “The uneven spread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hat do we know? Where do we look for answers?,” in Kathryn M. Neckerman, ed., Social inequality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3–77.
[2] 我们给出了1980—1982年、1990—1992年、2000—2002年、2010—2012年和2016—2018年每个时段的三年平均值。
[3]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 cal Economy , 110(4), 730–70.
[4] Robert D. Mare and Christopher Winship, 1991,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marriage for blacks and whites,” in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F. Peterson,ed., The urban underclass , Brookings Institution, 175–202.
[5] William Julius Wilson and Kathryn Neckerman, “Poverty and family structure: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Sheldon H. Danziger and Daniel H. Weinberg, ed., Fighting poverty: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32–59.
[6] Ansley J. Coale and Susan Cotts Watkins, 1986,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 Anthony Wrigley and Roger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 Edward Arnold.
[7] Sara McLanahan, 2004, “Diverging destinies: How children are faring unde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y , 41(4), 607–27.
[8] McLanahan; Kathleen Kiernan, Sara McLanahan, John Holmes, and Melanie Wright, 2011, “Fragile families in the US and the UK,” https://www .researchgate .net /profile /Kathleen _Kiernan3/publication/254446148 _Fragile _families _in _the _US _and_UK/links /0f31753b3edb82d9b3000000/Fragile-families-in-the-US-and-UK.pdf; Kelly Musick and Katherine Michelmore, 2018, “Cross-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union stability in cohabiting and mar-ried families with children,” Demography , 55, 1389–421.
[9] Andrew Cherlin, 2014, 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 ica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45.
[10] Guttmacher Institute, 2017, “Abortion is a common experience for U.S. women,despite dramatic declines in rates,” news release, October 19, https://www . guttmacher . org /news - release /2017/abortion-common-experience-us-women-despite-dramatic-declinesrates.
[11] 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J. Nelson, 2013, Doing the best I can: Fathers in the inner cit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Andrew Cherlin, 2009, The marriage- go- 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 ica today, Vintage Books/Random House, loc. 2881 of 4480, Kindle.
[13] Robert D. Putnam,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Simon and Schuster.
[14]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有关一般性说明,参见Gallup,“How does Gallup Daily tracking work?,”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9, https://www .gallup. com /174155/gallup-daily-tracking-methodology.aspx。
[15] Larry M. Bartels,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 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Gilens, 2012,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Robert D. Putnam and David E. Campbell, 2010,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Simon and Schuster.
[17]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
[18] Putnam and Campbell, American grace .
[19] Robert P. Jones and Daniel Cox, 2017, Ameri ca’s changing religious identity ,PRRI, https:// www.prri.org/research/american-religious-landscape-christian-religiouslyunaffiliated/.
[20] Robert Wuthnow, 1998, After heaven: spirituality in Ameri ca since the 1950s , Uof California.
[21] Cherlin, Marriage-go-round , loc. 485 of 4480, Kindle.
[22] Kathryn Edin, Timothy Nelson, Andrew Cherlin, and Robert Francis, 2019, “The tenuous attachments of working- class m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3(2),211–28.
[23] David G. Myers, 2008, A friendly letter to skeptics and atheists: Musings on why God is good and faith isn’t evil , Jossey-Bass/Wiley.
[24] Richard Layard, 2005,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 Penguin.
[25]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分别计算了受调者对各种感受的问题的答案。

★★★
★★★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记录了多种现象,包括绝望和压力、自杀身亡、滥用药物和酗酒,以及疼痛、对工作的依恋降低、工资的下降和家庭生活的失败。过去30年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人口中肆虐的这场“瘟疫”,在50多年前也曾横扫非洲裔美国人。随着种族分化在许多方面日渐消除,阶层分化现象正在不断加剧,至少在我们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阶层时是这样的。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我们将论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那么,到底是什么侵蚀了劳工阶层生活的基础?
第四篇是本书唯一附有绪论的篇章。其他三篇所讲述的,主要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本篇则讨论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而“为什么”总是比“什么”更复杂。本篇的前三章讲述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在劳动力市场的遭遇,以及他们收入的实际价值为什么会不断下降,是因为工资下降还是物价上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及为什么工作条件不断恶化。有多股力量正在破坏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工作环境,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记述的那样,这些力量会对婚姻和社区造成破坏性影响,并最终成为绝望的死亡人数暴增的温床。
我们的第一重叙事聚焦于美国特色,即美国资本主义独具的某些特征会使其忽视普罗大众的利益。其他一些富裕国家也出现了绝望的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但就算在那些确实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绝望的死亡的人数与美国相比也相形见绌。
当然,还有第二重叙事,即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存在问题,而美国只是一场更大规模灾难中的引领者,这场灾难在其他地方也已经扎根,并将在未来进一步蔓延。
我们怀疑,这两重叙事都反映了部分事实,美国的具体政策放大并助长了这场灾难,因此美国成为排头兵,而其他国家则紧随其后,但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出现同样严重的情况。
美国的制度有许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美国的种族历史与众不同。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阴影至今仍笼罩美国人的生活。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在许多白人眼中,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的改善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另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解释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与美国相比,其他富裕国家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而且它们的组织方式有所不同,更多依赖政府,而不是大量依赖私营部门。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十分独特,依赖大量的竞选资金和游说。
然而,我们眼中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上述方面,而是美国的医疗制度。这是第十三章的主题。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美国在医疗制度上的花费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和医生而自豪。世界各地的病人都慕名而来,在美国医院接受治疗。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会连续三年下降呢?其他国家都未出现这种现象,而这同样也是美国自一个世纪前的流感大暴发后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事实是,这种可怕的现象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现实给了美国的医疗制度太大压力,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存在问题,第十三章的论述将证明这一点。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医疗制度过差或覆盖不足,尽管关于这两点也有很多可以探讨之处。处方类阿片类药物致死是由医疗制度造成的,而且即使在实施了奥巴马医改计划后,仍然有27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1] 更严重的问题是医疗体系的巨大成本。在医疗保健领域投入的巨额资金严重拖累了经济,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并压低了工资,减少了优质工作的数量,影响了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对联邦和州政府提供(或本可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拨款。劳工阶层的生活无疑受到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威胁,但高昂的医疗费用无疑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下滑,并使这种下滑不断加速。
医疗费用就像是美国人不得不向一个外国强权支付的贡金。 [2] 它就好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支付的赔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撰写过一本著名的书,预言这些赔款将是一场灾难。 [3] 虽然历史学家们今天仍在争论赔款的实际数额到底是多少,以及赔款对魏玛共和国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崛起产生了何种影响,但很明显,赔款多年来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4] 然而,单以资金数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支付的赔款额远远低于美国在今天无谓地投入医疗体系的资金。 [5] 就算医疗制度能够保障国民健康(它事实上并未做到这一点),其巨大的成本也会削弱经济,尤其是经济中服务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口的部分。沃伦·巴菲特将医疗费用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比作绦虫,我们则认为它更像一种癌症,已经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并扼杀了经济满足美国人民需求的能力。
我们认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危机确实是造成没落和绝望的原因,但它绝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些证据指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越来越多地牺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利益,转而服务高学历的少数人。一个关键的论点是,企业积累了巨大的市场势力,并越来越多地将其用于对抗工人和消费者。他们的许多做法是反托拉斯法禁止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法律并未得到应有的大力执行。此外,工会曾经是重要的反制力量,抵御资本的力量,并保护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但现在,工会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特别是在私营部门。随着企业大量合并,美国企业间的竞争不再那么激烈,因而它们有权人为压低工人工资和提高产品价格。这些行为将工人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重新分配给企业经理人和资本的所有者。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政府不讲裙带关系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那么通过强力执行反托拉斯法,这种向上的再分配根本不会发生。
上述有关企业行为危害的观点在专业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和决策者之间引发了极大争议。一方面,有人声称现代大公司是垄断企业,使我们进入新的镀金时代,并导致消费者和劳工阶层深陷穷困。另一方面,也有人声称大公司因其带来的低廉价格和出色创新而令所有人都极大受益。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尽管欧洲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管的政策和美国不同。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即在美国,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会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出现和发展,因此引发了一种观点,即我们记录的美国困境只是一个先兆,未来将很快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无法在这里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的研究远未完成。相反,我们将努力在第十五章提供一个平衡的解释,至少努力找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哪些方面可能正在损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生活。
接下来的三章所论证的内容适用于所有美国人,而非仅仅是针对非西班牙裔白人。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至少直到芬太尼在2012年侵入黑人社区之前,绝望的死亡仍主要发生在白人之中。
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没有白人劳工阶层的毁灭,白人绝望的死亡就不会出现,或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反过来,如果没有医疗制度的失败和我们今天面对的资本主义的其他问题,尤其是通过操纵市场不断进行向上的再分配,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我们在第五章中曾指出,非洲裔美国人并不是逃脱了危机,而是早在30年前就经历了他们自己版本的危机。在黑人面临绝望、失业、家庭和社区破碎冲击的早期阶段,许多功能性失灵都被归因于黑人文化的特殊性。现在再回看这一幕,我们将会有些不同的发现。如果任何一个群体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击,那么它将很容易出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崩溃。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都是最不受欢迎的群体,他们也是第一个受害群体,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则紧随其后,成为下一个受害群体。假如设想这种痛苦会继续扩散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其实也并非天方夜谭。
黑人面对的种族仇恨不断降低,同时他们也逐渐拥有更多的机会,这抵消了他们面对的部分消极压力,而这些压力是所有劳工阶层均需要面对的。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中,非洲裔美国人口中出现了一些绝对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相对于白人的进步。至少在2014年之前,美国黑人的死亡率持续稳步下降。拥有学士学位的黑人比例从1945年出生队列中的16%,上升到1985年出生队列中的25%。 [6] 如果考虑教育因素,那么黑人在一系列生活满意度和影响方面的表现与白人持平,或者优于白人。然而,在近几十年的经济数据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黑人的物质收获相对于白人发生了任何系统性的改善。非洲裔美国人针对白人的相对进步一定来自其他地方。也许最明显的改善来源是黑人非物质层面的生活更好。虽然歧视远未消失,但歧视已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和普遍,种族歧视不再得到社会认可。衡量尊重性的一个极好指标是人们对跨种族通婚的接受度。黑人与白人通婚曾经是禁忌,现在则被认为是正常的。盖洛普的数据显示,2013年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87%的人赞成黑人与白人的婚姻。1958年,这一比例仅为4%。1973年,该比例也仅为29%,甚至在2000年也还不到2/3。盖洛普的调查员弗兰克·纽波特称,这是“盖洛普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意转变之一”。 [7] 现在已经出现许多成功的黑人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还出现了一位黑人美国总统。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异,曾经主要是肤色和种族歧视,现在则更多与教育和技能有关。
有人可能会表示,白人的特权逐步被取消,这对于白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反向歧视过程。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所写的那样,白人“直到他们的特权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以立法形式遭到削减之后,才开始审视自己的地位。在此之前,以白人权利为基础的旧有体制已经存在如此之久,以致他们已对此视而不见,在白人工人眼中,新的机会平等法并不像取消了某些种族特权,而更像在实施反向歧视” [8] 。经济学家伊莉亚娜·库兹伊姆科与合著者通过实验发现,无论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非常不喜欢落在最后,如果排在他们后面的群体看上去有可能超越他们,他们将会坚决抵制那些会改善排在其后多数人命运的变化。 [9]
最后,我们想解释我们是如何思考“为什么”的。我们更多的是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度思考事物的原因,这与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思考因果关系的方式截然不同。现在,有些经济学家鼓吹,要想证明因果关系,需要设计一个对照实验,或者至少存在某种历史环境,使得同一群人被分成不同群体,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分别暴露在同一个事件当中。这些技巧自有其用途,但它们在这里对我们基本毫无用处,因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缓慢发展的大规模解体过程,其中涉及一系列偶然的历史力量,而且许多力量相互作用。一些强调实证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虚幻的。 [10] 我们从根本上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读者将不得不决定,在没有受控性实验或任何类似做法的支持下,我们的论述是否有说服力。
[1]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18, “Key facts about the uninsured population,”December 7, https://www.kff.org/uninsured/fact-sheet/key-facts-about-the-uninsuredpopulation/.
[2] Victor R. Fuchs, 2019, “Does employment- based health insurance make the US medical care system unfair and ineffici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21(21), 2069–70,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9.4812; Victor R.Fuchs, 1976, “From Bismarck to Woodcock: The ‘irrational’ pursuit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19(2), 347–59.
[3] John Maynard Keynes, 1919,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Macmillan.
[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1986,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26.
[5] Max Hantke and Mark Spoerer, 2010, “The imposed gift of Versailles: The fiscal effects of restricting the size of Germany’s armed forces, 1924–2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63(4), 849–64.
[6]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7] Frank Newport, 2013, “In U.S., 87% approve of black- white marriage, vs. 4% in 1958,” Gallup, July25, https:// news.gallup.com/poll/163697/approve-marriage-blackswhites.aspx.
[8] Andrew J. Cherlin, Love’s labor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 ca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54.
[9] Ilyana Kuziemko, Ryan W. Buell, Taly Reich, and Michael I. Norton, 2014,“‘Last- place aversion’: Evidence and redistributive implic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29(1), 105–49.
[10] Alan S. Gerber, Donald P. Green, and Edward Kaplan, 2003, “The illusion of learning from observational research,” September10, https:// 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Donald_Green4 /publication/228755361_12_The_illusion_of_learning_from_observational_research/links /0046351eaab43ee2aa000000/12-The-illusion-of-learningfrom-observational-research.pdf.
美国人在医疗保健方面开销巨大,这些花费几乎影响经济的各个方面。医疗保健在世界各地都很昂贵,富裕国家在延长其公民生命和减少痛苦方面花费大量资金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美国的做法简直是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
我们不会重点讨论医疗过程中有时会发生的直接伤害,例如,医疗失误、不当治疗、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或在病人需要时未能提供治疗等,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医疗制度超乎寻常和极不恰当的费用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造成的间接伤害。美国的医疗制度吞噬了美国GDP的18%——在2017年为每人10739美元, [1] 约为美国国防开支的4倍、美国教育开支的3倍——毫无疑问,它也无端侵蚀了工人的工资。由于要支付医疗保险费用,这不仅减少了工人家庭可支配的工资收入,从而影响这些工资能够购买的东西,还使医疗行业的收入膨胀,并刺激了行业规模过度发展。雇主负担的医疗保险成本基本上不会被雇员看到,但它不仅压低了工资,而且还破坏了工作岗位,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工人的工作岗位,并以比较差的工作取代好工作。由于人们不得不从事更差的工作,他们的工资也随之下降。高昂的医保费用还直接打击了那些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个人,并影响了那些通过共同支付、免赔额和雇员供款获得医疗保险的人。它们还影响了联邦政府以及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州政府。各州政府必须征收更多的税款,减少美国贫困人口特别依赖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教育等其他方面的支出,或使用可能危及未来经济增长的财政赤字,将负担转移到我们的子女和未来的纳税人身上。
美国的医疗制度,借用亚当·斯密对于垄断的评论,可谓既“荒谬又具压迫性” [2] 。
医疗保健费用高昂本无可厚非,我们应该在医疗上面花费巨资也合情合理。为了获得更美好和更长久的寿命而放弃一些财富自有其必要性,而且这样做会使我们越来越富有。 [3] 延长寿命或提升生命质量的新疗法不断出现。它们的发明和实施可能也需要不菲的花费,而支付这些费用通常是明智的选择。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有太多不必要的花费。我们认为,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至少可以削减1/3的医疗费用。
正如我们在第九章论述阿片类药物时看到的那样,医疗行业的一部分——药品制造商和经销商——通过引发一场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流行病而发财致富。这是一个直接危害人们健康的极端例子,也是一个向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上层的少数人为了自己谋利而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其中许多人面临被辞退和死亡的危险。医疗行业必须对这种直接危害健康的行为负责,同时还应承担对整个经济造成间接危害的责任。意外过量使用药物导致死亡是三种绝望的死亡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种,其中大量案例都可归咎于医疗行业引发的阿片类药物流行病,尽管生活恶化导致一些人更易上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那些无论工作还是家庭生活都日益艰难的人口中,自杀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高昂的医疗费用则加速了这些死亡。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其他行业,以及它们在导致绝望的死亡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不仅因为它可以直接杀人,而且因为医疗行业的经济意义与其他行业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虽然自由市场竞争是衡量经济多个方面的良好基准,使我们可以依靠市场实现理想的结果,但对医疗行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自由市场竞争不能,也不会提供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医疗服务。 [4]
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在富裕国家中则是最差的,在近期出现的死亡流行病和预期寿命下降之前很久,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事实。提供医疗服务耗费的成本严重拖累了经济,导致工资长期停滞,这也是劫贫济富式再分配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曾将这种现象称为“诺丁汉郡治安官式”再分配。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擅长增进人民的健康,但它擅长增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财富,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成功的私人医生,他们经营着极其有利可图的业务。它还向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制造商、保险公司(包括“非营利性”保险公司)以及更具垄断性的大型医院的所有者和高管输送了巨额资金。
图13-1显示了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是如何扩大的。我们选择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和瑞士为比较国,代表其他富裕国家。 [5] 图中的纵轴和横轴分别为预期寿命和人均医疗支出,每条曲线是由1970—2017年,这两个数字在当年的交汇点连接而成的(人均医疗支出以国际元 [6] 计算,因此2017年美国的数字与此前所述的10739美元有所不同)。
在图13-1中,美国显然是异类。它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他国家要低,但人均医疗支出却高了很多。1970年,即曲线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的预期寿命并没有落后多少,医疗支出也没有高出许多,但在此之后,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推动了健康状况更快改善,并更好地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瑞士是图中和美国最相近的国家,其他国家的曲线则彼此十分贴近。如果图中再加上其他富裕国家,它们的曲线看起来也会更接近那些人均支出较低的国家,而不是瑞士或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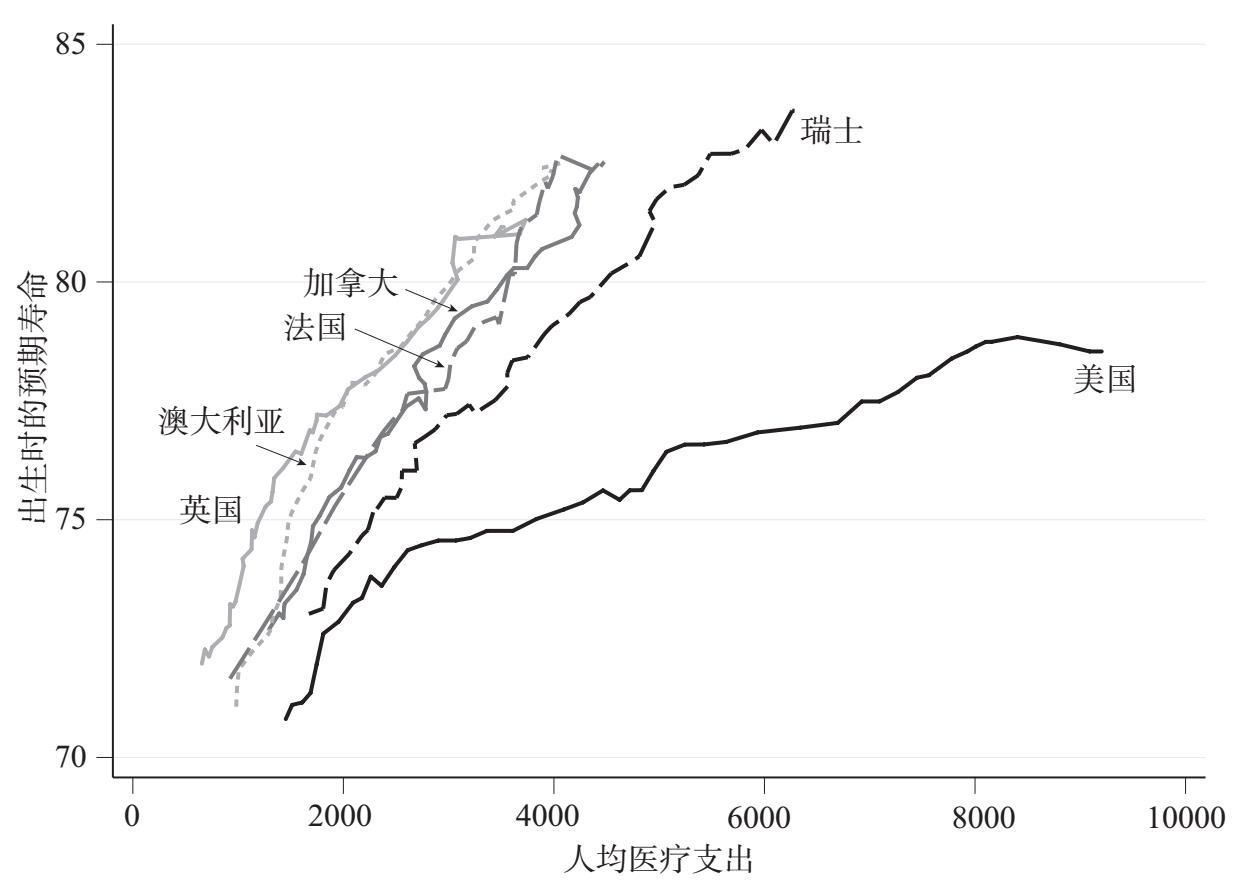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罗塞(2017)报告更新所得
2017年,瑞士的人均寿命比美国人长5.1年,而人均医疗支出却少了30%。其他国家的人均寿命与美国人相当,但人均医疗支出大大低于美国。2017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17.9%,其次是瑞士,为12.3%。假设有一位仙女能以某种方式将医疗支出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到位居第二的瑞士的水平(不需要雄心勃勃地将其降低到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美国将可以把其GDP的5.6%用于其他方面,并因此多出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资金。 [7] 这意味着美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年都多出3000美元以上的收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则每家大约能获得8300美元的额外收入。2017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6.1万美元,一个由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的贫困线为2.5万美元。如果在2017年,每个家庭都能获得8300美元的额外收入,那么过去30年的收入增长中值将达到实际增长率的两倍。冒着对我们的仙女提出太高要求的风险,假设我们再次提出要求,既然能降到瑞士的水平,为什么不能降到加拿大的水平呢?如果做到这一点,将节省1.4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人4250美元,每户11000美元。
另一种计算医疗费用浪费的方法是直接确定医疗支出中对美国人健康没有贡献的部分。最近的计算是, [8] 浪费的部分大约占总支出的25%,与美国和瑞士的差额大致相当。
这个极其巨大的数字是浪费额,而不是总费用。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浪费一点点逐渐侵蚀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美国的劳工阶层如果不必支付这笔贡金,他们今天的生活将会好很多。
考虑到如此高昂的费用,我们无疑希望美国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在预期寿命方面的表现并不算好,而预期寿命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除了医疗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预期寿命,但医疗水平在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2017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为78.6岁,西班牙裔人口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8岁),非西班牙裔黑人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4.9岁)。 [9] 这些数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25个成员国的预期寿命。在其他成员国中,德国的预期寿命最低,为81.1岁,比美国长2.5岁,日本的预期寿命最高,为84.2岁。 [10] 无论美国人从医疗制度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显然没有得到更长的寿命。
或许美国人有别的收获?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美国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而支付更多费用也很合理。然而,美国人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多地使用医疗服务,尽管医疗领域的工作岗位大幅增加。2007—2017年,医疗行业新增280万个就业岗位,占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1/3,这些新增就业岗位的资金主要来自非营利部门的“利润”。 [11] 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医生数量有所减少——美国医学会通过限制医学院的入学名额有效地确保了医生的高薪——人均护士数量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医学院的学费昂贵,这一点常常被用作说明医生有正当理由获得高薪,但如果医学院在没有名额限制的情况下接受竞争,费用无疑会降低。如果不是有体系地把合格的外国医生排除在外,医生的工资和医学院的学费都会下降。在实施某些治疗措施方面,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数字大致相同,尽管美国似乎更侧重于营利性的治疗措施。 [12] 美国人似乎拥有一个更豪华的体系(像是商务舱而不是经济舱),但无论乘坐商务舱还是经济舱,乘客总是会在同样的时间到达同一目的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目的地是来世,那么商务舱的乘客可能更快)。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病人相比,美国人等待手术(例如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或检查(例如乳房X光检查)的时间较短。等待时间较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有很多昂贵的机械设备没有得到大量使用。美国的病房大多为单人病房或双人病房,而其他国家的病房更常见的是多人病房。
发病率比死亡率或手术次数更难衡量,但有人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完全相同的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发现一系列健康状况指标(部分源于自我报告,部分来自通过化验血液得到的“硬”生化指标)表明,英国人在中年后的健康状况好于美国人。 [13] 英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不到其GDP的10%,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美国的1/3。
美国人对其医疗制度也并不满意。2005—2010年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只有19%的美国人对下面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即“你对医疗制度或医疗体系有信心吗”。 [14] 盖洛普还询问人们是否对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或地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感到满意。美国在这个更具体、更地方性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好,77%的人给出了肯定答复,与加拿大和日本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差于其他富裕国家,也不如一些更贫穷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如柬埔寨、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瑞士,94%的人对本地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表示满意,58%的人认为国家医疗制度或医疗体系运作良好。美国人的不满主要集中于在一个不公平的体系中获得医疗服务。根据联邦基金于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获得医疗服务、患者安全、协调、效率和公平”方面,美国在7个富裕国家中排名垫底。 [15]
美国人付出了这么多,但获益却这么少,这怎么可能?这些钱肯定花在了什么地方。病人花的冤枉钱变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在这里再次和其他富裕国家进行比较依然会很有用。医疗费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医疗服务价格更高,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更高。美国医生的工资几乎是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医生平均工资的两倍。 [16] 不过,由于医生人数相对于总人口数量下降,他们在高昂的医疗费用中所占份额有限。 [17] 应医生团体和国会的要求,医学院的招生人数受到严格控制,同时外国医生难以在美国执业。 [18] 200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中,医生占16%。在这1%的前10%中,有6%是医生。 [19] 美国护士的收入也相对较高,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大。在美国,药物的价格大约是其他国家的3倍。 [20] 在美国,服用降胆固醇药物瑞舒伐他汀每月需要花费86美元(打折后),该药在德国的月度花费是41美元,在澳大利亚只有9美元。如果你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你的修美乐(阿达木单抗)在美国每月需要花费2505美元,在德国是1749美元,在澳大利亚是1243美元。美国的手术费用更高。在美国,髋关节置换术的平均费用超过4万美元,而在法国,同样手术的花费大约为1.1万美元。在美国,即使同一制造商生产的相同设备,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的费用也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以上。磁共振成像检查在美国要花费1100美元,但在英国只需要300美元。美国医生需要支付的医疗事故保险费用也更高,尽管与医院费用(33%)、医生费用(20%)和处方药费用(10%)相比,它只占医疗费用总额的2.4%,这并不算多。 [21] 相对于其他富裕国家,美国的医院和医生更多地使用“高利润率和高金额”的治疗措施,如影像学检查、关节置换、冠状动脉搭桥术、血管成形术和剖宫产。 [22] 2006年,我们两人中的一位更换了髋关节。当时,纽约一家著名的医院对一间(双人)病房的收费高达每天一万美元。病人在这间病房中能够饱览东河上船只如梭的美景,但电视节目是额外收费的,更不用说药物和治疗了。
美国制药公司的捍卫者认为,大部分药物研发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尽管并不总是由美国公司完成的),因此其他国家都在免费享用美国的创新和科学发现。批评人士则指出,制药公司在市场营销上的投入远大于研发投入,许多基础研究是由政府完成或资助的(例如,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他们还指出,缩短甚至取消专利保护可能不会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3] 现行体制在很多方面根本站不住脚。以胰岛素为例,如果没有胰岛素,糖尿病患者将会死亡,胰岛素的三位发明者以每人一美元的价格将这一发现卖给多伦多大学,以保证它可以被永久免费使用。然而,一些患者现在不得不每月支付高达1000美元的费用,有时甚至只能放弃治疗,而制药厂商则通过调整药物配方维持其专利。 [24] 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制药公司已经设立大规模的慈善基金会,通过承担病人共同支付部分的费用,使其更容易维持药物的高价格。更重要的是,制药公司通过慈善基金会承担的每一美元共同支付费用,都可以享受两美元的税收减免。 [25] 如果可以降低药品价格,则可以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规模扩展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它还将节省大量资金,并减轻我们在提供其他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时面临的压力。
除了价格,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因素。新药、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其中有些可以拯救生命、减少痛苦,但很多并没有什么效果,但它们依然被推给病人并收取费用。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医疗”,即投入更多资金并未带来更大程度的健康增长。与美国不同,英国设置了监管机构,即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这个机构负责评估新药和新的治疗手段,预估每多花一英镑会带来多少额外健康,并且在这些药物或治疗手段没有达到最低收益要求时建议不使用它们(考虑到英国的体制,这实际上彻底使它们出局)。在美国,这样一个机构将直接威胁医药行业的利润,因此行业将拼死反抗,这也就意味着这家机构肯定会死,而不是行业会死。
NICE的第一任主席迈克尔·罗林斯爵士表示,NICE首个测试的药物是瑞乐沙,这是由原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治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NICE建议不要使用它,不是因为它没有效果,而是因为它的“外部”影响,医生办公室里等待处方的流感患者会传播疾病。该公司的主席“冲进唐宁街,威胁要把他的研究带出国”。但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力挺NICE,使该机构免于胎死腹中。 [26] 我们怀疑,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华盛顿,最终的决议则可能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想提请读者注意,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药品审批过程中不被允许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阿片类药物可能被转售的影响。
医疗保险公司经常受到媒体的批判,尤其是当他们拒绝支付治疗费用,或者向那些认为自己已有全额保险的病人寄去令其费解的账单时。这里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私营系统中,保险公司、医生诊所和医院在管理、谈判费率和试图限制开支方面花费了巨额资金。而一个单一付款人系统,尽管根据设计不同可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但至少会节省一半以上的类似费用。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源不仅在于保险公司追求利润,如果医疗制度的运行方式不同,保险公司就可以省去现在所做的大部分工作。 [27]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医院提高价格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而是因为它们正在进行整合,从而减少或消除了竞争,并利用强大的市场势力提高价格。它们正在稳步赢得与保险公司(和公众)的战争。与面临竞争的医院相比,地方垄断性医院的收费要高出12%。此外,当一家医院与5英里内的另一家医院合并后,医院之间的竞争会减弱,而医疗服务价格会平均上涨6%。 [28]
患者在出现急症的情况下最容易处于弱势地位,而医疗急症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和作为赢利机会。救护车服务和急救室已经外包给医生与救护车服务公司,这些医生和救护车每天都正在发送“出人意料”的医疗账单。这些服务中的许多项目并不在医保范围之内,因此即使患者被送往自己的医疗保险覆盖的医院,也需要自己支付各种急救费用。2016年,很大一部分急诊室就诊病人支付了“意外”的救护车费用。随着农村地区医院的关闭,空中救护车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们可能会带来数万美元的意外费用。当有人陷入困境,甚至失去意识时,他们没有能力就收费高低讨价还价,同时,由于不存在能够抑制价格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意识尚存,病人也只得乖乖按要求付钱。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许多由私人股权公司所有,它们非常清楚这正是漫天要价的理想情况。 [29] 现在,那些追在救护车后面寻找获利机会的事故官司律师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救护车的拥有者,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医院醒来时,会一眼看到他们的轮床上贴着2000美元的账单。
这种掠夺是一个典型例子,表明一个向上转移收入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情况下,金钱从身处困境中的病人手中转移到私人股权公司及其投资者手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资本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拥有诸多优点,但却不能以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在医疗急症情况下,人们无法做出竞争所依赖的知情选择,正如人们在陷入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时,无法做出知情选择一样。
过去由医生管理的医院现在已经改由企业高管管理,其中有些人是脱下白大褂并换上西服套装的医生,他们领着首席执行官的薪水,追求的是建立商业帝国和提高价格的最终目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由多家曾经独立的医院组成的庞大医院集团。长老会医院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其首席执行官史蒂文·科温博士在2014年的薪酬高达450万美元, [30] 而纽约北岸大学医院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其薪酬的两倍。 [31] 纽约长老会医院推出了一系列制作精美的视频故事广告,这些广告在大受欢迎的《唐顿庄园》系列剧集播出之前在公共电视上播放,每一个广告都记录了一个只有在纽约长老会医院才能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康复故事。 [32] 这些广告的目的是诱导员工要求将这家医院纳入他们的保险计划,使医院增加与保险公司谈判的能力,这有助于它提高价格,从而使科温的高薪获得保证。其他医院很快效仿,推出了类似的广告。2017年,美国医院在广告上花费了4.5亿美元。 [33] 很难看出这些策略能怎样改善患者的健康。
医生、医院、制药厂商和设备制造商通力合作,共同推高价格。高科技医用扫描设备的制造商向医生、牙医和医院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租赁和定价条款,后者使用设备,为各方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但并不会给病人带来明显的效果改善。或许,扫描设备(scanner)和骗子(scammer)的英文名难以区分并不是巧合。制药厂商也会与医院和医生合作,帮助它们开发新产品,并提高需求。2018年,著名乳腺癌研究专家何塞·贝塞尔加被迫辞去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医院的首席医疗官一职, [34] 该医院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私人癌症治疗中心。贝塞尔加被迫辞职的原因是他未能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披露潜在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来自他与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和制药公司千丝万缕的财务联系。在他辞职后,这些利益冲突方中的一家——阿斯利康公司立即任命他为公司的研发主管。正如医院管理层所说(他们说的完全正确), [35] 医院在为病人提供新药试验,或者医生尝试帮助传播关于有效新产品的信息时,存在潜在的利益共生关系。事实上,新的癌症药物近年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由于患者的最大利益并不总是与制药厂商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他们自然可能想知道他们的医生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并需要确信他们的医院不仅仅是制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
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薪水都颇为丰厚。根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的一份报告,2017年,在薪酬收入排名前十的CEO中,收入最高的是艾瑞·鲍斯比,他的年薪为3800万美元,他是艾昆纬公司的CEO,该公司是一家为制药公司、保险公司和政府提供患者信息分析服务的数据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默克公司的CEO肯尼斯·弗雷泽,年薪1800万美元。 [36] 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部分是来自小型私营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而这些收入丰厚的小型私营企业主中,不乏私人诊所的医生。 [37]
美国医疗服务的超额费用流向了医院、医生、设备制造商和制药厂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这些费用是一种浪费和滥用,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它则是一笔丰厚的收入。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这些费用会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业是如何做到全身而退的?
从机械的角度理解费用由谁支付并不复杂,但要弄清楚其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则困难得多。最后,不管是谁拿到的账单,最终所有费用都将由个人支付,所以我们应该牢记一个数字,即美国人均医疗总成本达10739美元。许多美国人对他们需要付出这样一大笔钱,或者人均需要付出这笔钱,感到不可思议。这些账单通常由保险公司、雇主或政府支付,我们大多数人都比较幸运,从来没有收到过医疗账单,甚至没有见到过一张让我们伤筋动骨的医疗账单。然而,正是由于缺乏透明度,以及其他人会帮我们付这笔钱的普遍感觉,才会出现当前的医疗制度,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制度的实际影响,那么它将受到更有力的挑战。 [38]
图13-2显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医疗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从1960年的5%增长到2017年的18%。另一个与此相反的数字可能同样有用,甚至可能更有用,那就是,GDP中可用于除医疗外的其他项目的支出从1960年的95%下降到今天的82%。图中还显示了医疗负担增长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及从2000年到2008年。正如伊齐基尔·伊曼纽尔和维克托·福克斯所指出的, [39] 这些时期正是平均时薪表现糟糕的时期,特别是与90年代中期相比更明显,90年代中期,工人时薪数据表现良好,但医疗支出的比例则有所下降。如果我们看一下45~54岁且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的状况,他们在2017年的平均工资比1979年低了15%,同样的状况还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工资又出现迅速下降,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过去几年有所回升。当然,工资高低受很多因素影响,尤其受更普遍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影响,同时医疗费用的上涨又是一个持续缓慢的过程,因此,这种跨越几十年的模式可能是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的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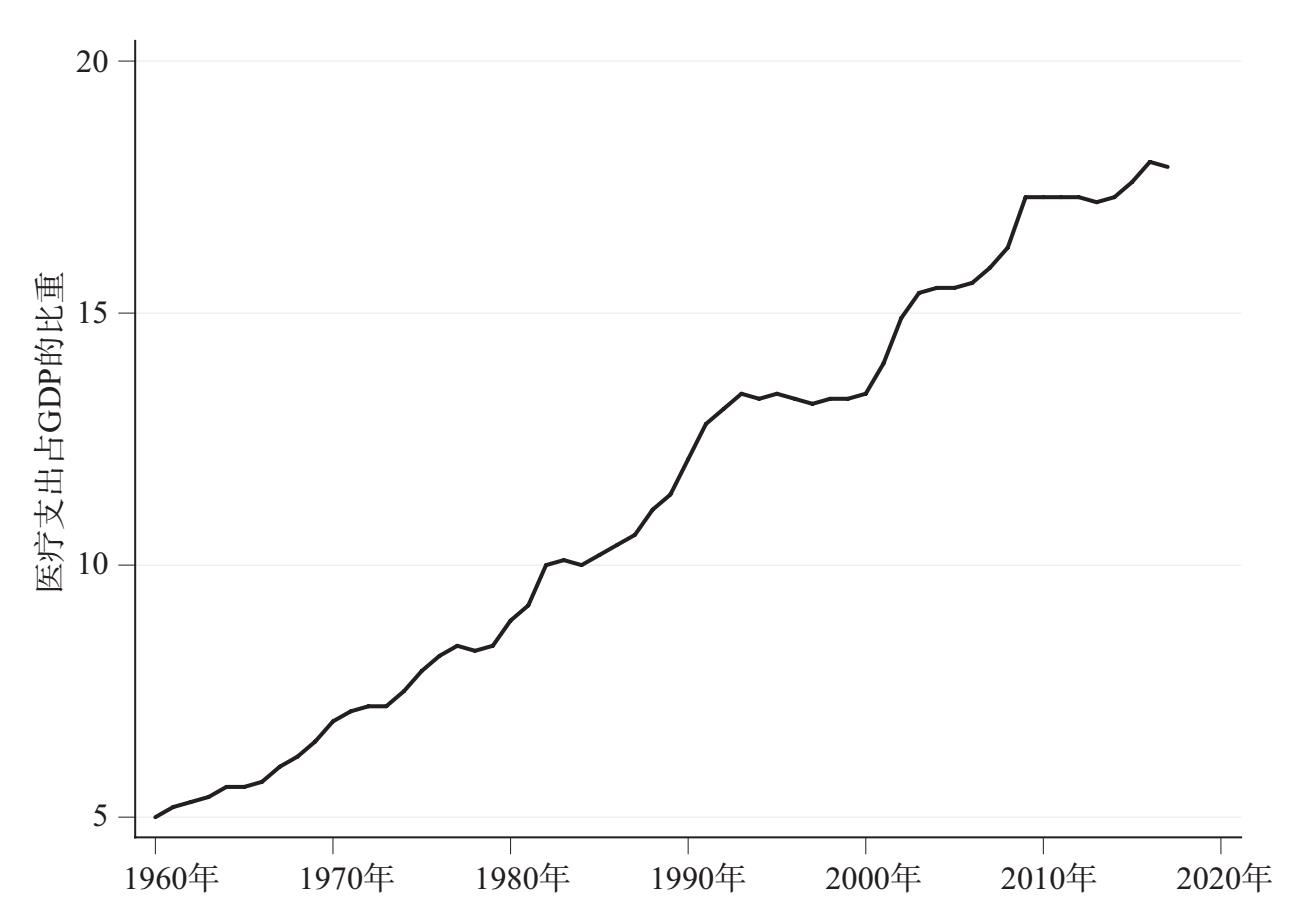
资料来源: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服务中心
如果我们从谁来付钱开始着手,会发现个人和联邦政府各付28%,另有20%由企业为其员工支付,17%由州和地方政府支付,其他私人付款人支付剩下的7%。 [40] 没有保险的人口(2017年,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9%,即2970万人)必须直接支付费用,且费率通常比向政府或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率高得多。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可能会得到慈善医疗,或者得到相互津贴的补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会被讨债人追上很多年。人们经常说,医疗保险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你的健康,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你的钱包免于被医疗体系掏空。没有保险的人往往会放弃非紧急治疗。如果没有找医生看过病,他们就不太可能使用像降压药或他汀类药物这样可以救命的预防性治疗。由个人负担的那部分医疗费用降低了人们购买其他物品或为未来储蓄的能力,这也成为导致美国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41]
大约一半工作年龄的美国人(约1.58亿人)通过雇主购买了医疗保险, [42] 同时65岁以上人口可以参加联邦政府付费的医疗保险计划。医疗补助计划则是针对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国家医疗计划,其费用部分由联邦政府承担,部分由州政府承担。
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通常很受被保险雇员欢迎,尽管它对雇员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成本。2017年,员工平均负担的费用约为1200美元(个人保单费用的18%),或5700美元(家庭保单费用的29%)。 [43] 此外,他们还需要支付医疗相关的税费,并且必须在治疗时支付共同支付费用,以及在报销前需扣除的所有费用。病人通常很难事先知道治疗费用是多少,或在事后了解具体账单。例如,保险公司可能会承担某项治疗90%的费用,而这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内部价格的90%,其实际费用可能远低于账单上的金额。对于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来说,突然收到出乎意料的医疗费用账单是常见现象,甚至在非急诊的情况下也经常发生。与此同时,在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在质量和保障范畴方面都正在恶化。 [44]
一项研究重点分析了截至2009年的10年的情况,在此期间,一个拥有雇主医疗保险的四口之家收入中值从76000美元增长到99000美元。但在增加的收入中,除了95美元之外,其余的钱都被员工保险费、医疗中自付部分的支出、医疗保险税以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抵消了。 [45]
雇主提供的保险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接受保险的员工并不总是清楚这些问题。许多雇员认为雇主承担的71%保险费用,即(平均)20000美元的家庭保险费用,对于他们而言是完全免费的。然而,由于对企业而言这笔费用是实实在在的支出,它会影响企业准备支付多少工资和雇用多少工人。雇主在做出雇用决定时,需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员工的工资,而是公司雇用员工必须支付的总成本,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费用。像员工工资一样,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费用也是员工薪酬成本的一部分,因此,保险费成本的上升,例如,从1999年的2000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6896美元(个人计划平均保险费用),是导致工资被压低的重要原因。员工可能会认为他们得到了一份礼物,却很少意识到雇主关心的是他们为每位员工支付的成本总额,而不论这些钱最终到了谁的手上。雇员可能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从他们的工资中部分或全部扣除的。 [46] 在上述例子中,如果雇主承担的保险费用没有上涨,一个四口之家在2009年本有可能得到高于9.9万美元的年收入。
事实还远不仅止于此。面对医疗保险费大幅上涨的情况,雇主可能决定不再为一些职位提供医疗保险,或者更进一步,他们可以雇用更少的工人,或者至少将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一位高管向我们解释说,有一年,当他的公司看到大幅增长的医疗保险费用时,聘请了管理顾问来帮助削减“总人头”,确定哪些员工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公司在餐饮服务、安保、清洁、运输方面的工作是否可以外包。这样,就可以把支付工资和医疗保险费用的责任转嫁给外包公司,由外包公司决定是否向员工提供这些福利。与为大公司工作相比,为外包公司工作往往是一个没有吸引力和缺乏意义的选择。医疗费用在低薪工人的总工资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对于年薪15万美元的高薪员工,家庭医疗保险平均只增加了不到10%的雇用成本;对于年薪只有工资中位数的一半的低薪员工,家庭医疗保险增加的成本则高达60%。这是医疗费用上升把好工作变为差工作,乃至彻底消灭工作的方式之一。
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导致医疗费用上涨,并使医疗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拥有较高技能和较高收入的就业者更有可能拥有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条款时主要考虑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口味。由于雇主承担的保险费用不被视作应税收入,因此雇主也有动力通过(不应税的)保险提供越来越豪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让雇员从税后收入中支出相关费用。这不仅使联邦政府损失了约1500亿美元的税收, [47] 而且还鼓励雇主和雇员在协商薪酬时包含更高端的医疗保险。正如维克托·福克斯指出的,政府似乎在全力促成“全食”式的医疗,而不鼓励“沃尔玛”式的医疗,尽管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从费用角度考虑更愿意获得后者。基于雇主的医疗保险制度无论在获取医疗服务方面,还是在服务内容上,都更偏向于高收入的就业者。 [48]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会承担医疗费用。对联邦政府来说,医疗福利费用必须与政府计划或有能力做的所有其他项目进行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未能维护和更新基础设施。由于美国糟糕的道路状况,联邦快递公司的运货卡车更换轮胎的频率已经达到20年前的两倍。 [49] 医疗补助计划给州政府在预算制定中带来的负担可能更加隐蔽。由于医疗补助是一项权利,各州别无选择,只能支付发生的医疗费用。除了在确定资格要求方面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外,各州对医疗服务内容或医疗费用的控制有限。在州一级,医疗支出的增长也同样侵蚀了其他重要的福利,特别是教育和交通。2008年,医疗补助计划支出占州政府支出的20.5%,到2018年,它已经增长到约29.7%,而同期中小学教育支出则从22.0%下降到19.6%。目前,各州在医疗补助计划上的支出达到在基础教育(K-12)上支出的一半。 [50] 而这个福利对那些经济能力雄厚,可以不依赖公立基础教育的人口而言显然不是那么重要。
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准确计算谁在为医疗费用买单,但其数额如此庞大,如此分散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并且如此不透明,因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为此买单,无论是以更直接的方式,还是(通常)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式。更糟糕的是,彻底了解成本后,我们发现,我们花钱时很少有意识地主动选择,并且也并没有把钱花在我们确实需要并愿意支付的方面。相反,医疗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的寄生虫,就像沃伦·巴菲特所说的绦虫,美国人很早以前不小心吞下了它,而现在它已经长得很大,正在消耗身体其他部分所需要的营养。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过去仅限于医疗系统的癌症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个经济中。
世界各国在为医疗保障提供资金和具体实施方面都面临极大困难,而不仅仅是美国面临困局。对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医疗服务。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思·阿罗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定理,向我们揭示了市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阿罗定理更精确地解释了亚当·斯密在很久之前提出的论点。并非巧合的是,阿罗还撰写了“健康经济学”领域的专著, [51] 阐述了为什么市场化的医疗解决方案从社会角度看并不可取。当然,正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加之强力实施的反垄断法)肯定能够带来比现在更低的价格。但医疗服务与其他服务不同。由于患者无法获得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的信息,这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对方掌控。我们无法抵制医疗服务提供商推动的过度供给。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汽车修理工身上,只不过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在市场上购买金枪鱼、汽车、住宅、机票等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很快就能知道哪些产品适合他们,哪些不适合他们,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将淘汰那些有缺陷或没人想要的商品或服务。假设你想要找到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在前面曾提到,我们中的一人做过髋关节置换术,当时在寻找外科医生时,我们尽可能地和每个人交谈,并尽可能地查阅资料,但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最喜欢的一个评论是,“他曾经为教皇做过手术,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手术后,一名夜班护士(她恰好名叫卡珊德拉 [52] ,尽管我们对事件的回忆可能受到了镇痛泵的影响而有失准确)简单讲述了她的看法,但可能病人和护士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显然速度给卡珊德拉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我们发现,一位骨科医生朋友自己的膝关节置换术居然失败了,这让我们明白,就算一位好的骨科医生也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在一个不受监管的市场上,医疗保险无法有效运作,甚至根本无法运作。由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双方面都有动力加大医疗支出,这将推动医疗保险费用不断上涨,并使其超出保险的购买者,尤其是相对健康的人愿意支付的范围。于是,较为健康的人会选择退出他们并不需要的昂贵保险,留在保险计划中的,将是一个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支出越来越大的群体,从而使保险计划难以为继,即出现臭名昭著的“死亡螺旋”。
医疗保险要想良好运转,加入保险计划的人必须既包括生病的人,也包括健康的人,这在美国是通过雇主提供保险实现的,在其他富裕国家则是通过政府法令要求全民参保实现的。如果没有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或者强制购买,保险就无法运作,或者只能提供给那些健康和不需要保险的人。把医疗服务完全交给市场,而没有任何社会支持和控制,将使许多人失去保险,并且在他们生病时得不到医疗服务。不受监管的市场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在病人最脆弱,即在他们面临紧急医疗状况时,私人股本公司对他们趁火打劫。
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不愿意接受政府对医疗实施管控,因为有时这些管控措施会相当严厉。他们乐于相信医疗制度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尽管政府支付了一半的费用,并且是没有经过谈判就支付了制药厂商开出的价格(通常被荒谬地描述为“市场定价”),同时政府不断授予医疗设备和药品专利,允许专业协会限制供给,并通过税收制度补贴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政治事实,即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付了多少钱。如果每个美国人每年在纳税时收到10739美元的账单,或者如果雇主将他们承担的雇员医疗保险费用从员工工资中扣除,那么改革的政治压力肯定会加大。隐形费用会鼓励过度收费。因为它们是隐形的,所以与某些更明显的问题,如美国几乎10%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障相比,这些费用带来的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后者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们在其他任何一个富裕国家都不会看到,但正是爆炸式增长的医疗费用,摧毁了国民经济为低技术水平工人提供医疗保障的能力,而这本是它应尽并且可以尽到的职责。
医疗服务提供者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防线,并且其还起到了攻击的作用,那就是华盛顿的医疗游说团体。游说行为不仅局限于医疗领域,它在我们的论述中占据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将在第十五章再次讨论它。目前,我们暂且只关注医疗领域。在医疗领域,正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企业的游说力度在过去40年急剧加大。它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将权力从劳动者手中夺走,将其重新分配给资本,以及从工人和消费者手中夺走权力,将其重新分配给企业和富有的专业人士。游说和寻租并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代表小企业的行业协会,如美国医学协会(拥有25万会员)和美国验光协会(拥有4万会员)是两个典型例子,这些协会的会员来自美国各地,从而使它们和国会的每位议员都能搭上话,并拥有来自家乡的有效政治力量来支持它们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扶持,共同以牺牲患者为代价,不断增加协会会员的利润。 [53]
2018年,医疗行业雇用了2829名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被超过5个说客包围。超过一半的说客是“反水者”,即前国会议员或前工作人员。一些人甚至戏称国会是为投身游说业做热身的“农场联盟” [54] [55] 。2018年,企业在游说上的花费高达5.67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制药厂商。 [56] 医药行业已经成为游说支出最大的行业,甚至超过金融业,其游说费用是工会组织的10倍有余。此外,医药行业还斥资1.33亿美元支持现任或潜在国会议员,投入7600万美元支持民主党,5700万美元支持共和党。许多游说活动都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过,当医疗问题摆在桌面上时,游说者也抓住机会帮助起草和通过对行业有利的立法。在立法者和他们的工作人员需要获取信息和做出分析时,说客们处于作为专家顾问的有利地位。美国也曾经设立一个独立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其作用与英国的NICE类似,但它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被关闭,纽特·金里奇是此事的主要推动者。
我们当然不是说,医疗行业可以为所欲为,游说团体也并不总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游说团体自身的立场也往往各不相同。不过我们尚未看到有效的游说团体,或者实力和规模可以与医药行业抗衡的游说团体,愿意为那些无奈买单,从而使医疗行业大发横财的患者发声,或者为能够充当反抗医疗行业的力量发声。
在立法活动期间,医疗行业的游说团体有时会非常有效。国会通过的奥巴马医改方案就完全没有考虑单一付款人制度或公共选择权,美国也没有建立英国那样的评估体系。医院、医生和制药公司都得到了有效的回报,以换取其对通过《平价医疗法案》的支持。 [57] 尽量将更多未参保人员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固然十分必要,但该法案阻止了任何控制成本的行动,鉴于游说团体强大的力量,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法案获得通过所需的必要妥协。医疗行业得到立法保护的另一个绝佳例子是,美国的医疗保险计划会为所有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物支付费用,并且不会就价格进行谈判(医疗行业曾长期反对医疗保险计划覆盖药物费用,理由是担心医疗保险制度会压低药品价格,但随着游说团体的数量和力量不断增强,它后来改变了立场,并争取到我们今天面对的更有利于医疗行业的安排)。 [58]
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本是一个历史的意外,现在它已经成为改革的巨大阻碍。这个制度诞生的那一刻就是绦虫被吞下,第一个细胞发生癌变的时候。不过,医疗行业在华盛顿备受呵护的现实也是医疗行业持续获得巨额收入和利润的关键,同时,代表医疗行业的游说团体完全有能力阻击任何可能的威胁。这就好比一个店主被要求支付保护费,于是他威胁对方要报警,结果他得知,来收保护费的敲诈者本身就是警察。美国的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这种敲诈勒索是当今美国出现劫贫济富的诺丁汉郡治安官式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医疗本来应该是改善人民健康的行业,而它却正在损害我们的健康;国会本应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它却正在支持医疗业对人民进行勒索。 [59]
[1] Anne B. Martin, Micah Hartman, Benjamin Washington, Aaron Catlin,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Accounts Team, 2019, “Nationa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in 2017: Growth slows to post- Great Recession rates; share of GDP stabilizes,” Health Affairs , 38(1), 96–106, https://doi.org/10.1377/hlthaff.2018.05085.
[2]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 bk. 4. See our introduction.
[3] Robert E. Hall and Charles I. Jones, 2007,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rise in health spend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22(1), 39–72, https://doi.org/10.1162/qjec.122.1.39.
[4] Kenneth J. Arrow,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 can Economic Review , 53(5), 941–73.
[5] Authors’update of Max Roser, 2017, “Link between health spending and life expectancy: US is an outlier,” Our World in Data, May 26, https://ourworldindata .org /the - link - between -life-expectancy-and-health-spending-us-focus. The underlying data used for extension are from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 worldbank . org / data - catalog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ata, data https://stats.oecd.org/.
[6] 国际元是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以方便比较。——译者注
[7] Victor Dzau, Mark B. McClellan, Michael McGinnis, et al., 2017, “Vital directions for health and health care: Priorities from a National Acad emy of Medicine initiative,” Journal of the Ameri 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7(14), 1461–70,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7.1964.
[8] William H. Shrank, Teresa L. Rogstad, and Natasha Parekh, 2019, “Waste in the US health care system: Estimated costs and potential for saving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 tion , 322(15), 1501–9,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9.13978.
[9] Elizabeth Arias and Jiaquan Xu, 2019, “United States life tables, 2017,” National Vital Sta tistics Reports , 68(7), https://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8/nvsr68_07-508.pdf.
[10] OECD.Stat, 2019, “Health status,” last updated July2, https:// 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HEALTH_STAT.
[11] Jonathan Skinner and Amitabh Chandra, 2018, “Health care employment growth and the future of US cost contai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9(18), 1861–62.
[12] Irene Papanicolas, Liana R. Woskie, and Ashish K. Jha, 2018, “Healthcare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ther high- 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19(10), 1024–39,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8.1150; EzekielJ. Emanuel, 2018, “The real cost of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19(10), 983–85.
[13] James Banks, Michael Marmot, Zoe Oldfield, and James P. Smith, 2006, “Disease and disadvan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ngl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295(17), 2037–45.
[14] Authors’calculations, Gallup World Poll.
[15] Karen Davis, Cathy Schoen, Stephen Schoenbaum, et al., 2007,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An international update on the comparative perfor mance of American Health Care , Commonwealth Fund, https://www.commonwealthfund.org/publications/fundreports/2007/may/mirror -mirror-wall-international-update-comparative-performance.
[16] Papanicolas et al., “Healthcare spending.”
[17] Emanuel, “Real cost.”
[18] Dean Baker, 2016, Rigged: How globaliza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economy were structured to make the rich richer ,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 Jon Bakija, Adam Cole, and Bradley T. Heim, 2012,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 April, https://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BakijaColeHeimJobsIncomeGrowth TopEarners.pdf.
[20] Papanicolas et al., “Healthcare spending.”
[21] Michelle M. Mello, Amitabh Chandra, Atul A. Gawande, and David M.Studdert, 2010, “National costs of the medical liability system,” Health Affairs , 29(9),1569–77, https://doi.org /10.1377/hlthaff.2009.0807; Martin etal., “Nationa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22] Emanuel, “Real cost,” 983.
[23] Baker, Rigged .
[24] Danielle Ofri, 2019, “The insulin wars: How insurance companies farm out their dirty work to doctors and patient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8.
[25] Economist , 2019, “Why Ameri ca’s biggest charities are owned by pharma ceu ti -cal companies,” August 15.
[26] Nicholas Timmins, 2009, “The NICE way of influencing health spend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ir Michael Rawlins,” Health Affairs , 28(5), 1360–65, 1362, https://doi.org/10.1377/hlthaff.28.5.1360.
[27] Emanuel, “Real cost.”
[28] Zack Cooper, Stuart V. Craig, Martin Gaynor, and John van Reenen, 2019, “The price ain’t right? Hospital prices and health spending on the privately insu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 nomics , 134(1), 51–107, https://doi.org/10.1093/qje/qjy020.
[29] Zack Cooper, Fiona Scott Morton, and Nathan Shekita, 2017, “Surprise! Out- ofnetwork billing for emergency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623, July; Eileen Appelbaum and Rosemary Batt, 2019,“Private equity and surprise medical billing,”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September 4, https:// www .ineteconomics.org/perspectives/blog/private-equity-andsurprise-medical-billing; Jonathan Ford, 2019, “Private equity has inflated US medical bills,” Financial Times , October 6.
[30] Steven Brill, 2015, Ameri ca’s bitter pill: Money, politics, backroom deals, and the fight to fix our broken healthcare system , Random House.
[31] David Robinson, 2016, “Top 5 highest paid New York hospital officials,”Lohud .com, June2, https:// www.lohud.com/story/news/investigations/2016/06/02/hospitals-biggest -payouts/85049982/.
[32] 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2017, “Amazing things are happening,” https://www .nyp.org/amazingthings/.
[33] Shefali Luthra, 2018, “Playing on fear and fun, hospitals follow pharma in direct- to- consumer advertising,” Kaiser Health News, November19, https:// khn.org/news/hospitals -direct-to-consumer-health-care-advertising-marketing/.
[34] Katie Thomas and Charles Ornstein, 2019, “Top cancer doctor, forced out over ties to drug makers, joins their rank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7, https:// www.nytimes.com/2019/01/07 /health/baselga-sloan-kettering-astrazeneca.html.
[35] Katie Thomas and Charles Ornstein, 2018,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s season of turmoil,”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31, https:// www.nytimes.com/2018/12/31/health/memorial -sloan-kettering-conflicts.html.
[36] Patrick Thomas, 2018, “Ever heard of Iqvia? Its CEO made $38 m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 June12, https:// www.wsj.com/articles/ever-heard-of-iqvia-its-ceo-made38-million-1528801200.
[37]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2019, “Capi tali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4), 1675–1745.
[38]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8,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 last modified April17, https:// www.cms.gov/Research-Statistics-Data-and-Systems/Statistics -Trends-and-Reports/NationalHealthExpendData/index.html.
[39] Ezekiel J. Emanuel and Victor R. Fuchs, 2008, “Who really pays for health care?The myth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9(9), 1057–59.
[40] Martin et al., “Nationa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41] Yi Chin, Maurizio Mazzocco, and Béla Személy, 2019, “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the U.S. saving rate: The role of health expenditu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0(4), 1–37, https:// doi.org/10.1111/iere.12405.
[42] Sara R. Collins, Herman K. Bhupal, and Michelle M. Doty, 2019,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eight years after the ACA,” Commonwealth Fund, February 7, https://www .commonwealthfund.org/publications/issue-briefs/2019/feb/health-insurancecoverage-eight -years-after-aca.
[43] Martin et al., “Nationa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44] Collins et al.,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45] David I. Auerbach and Arthur L. Kellerman, 2011, “A decade of health care cost growth has wiped out real income gains for an average US family,” Health Affairs , 30(9),1630–36.
[46] Jonathan Gruber, 2000,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Anthony J.Culyer and Joseph P.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 Elsevier Science,vol. 1, pt. A, 645–706, https://doi.org/10.1016/S1574-0064(00)80171-7.
[47]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2018, “Estimates of federal tax expenditures for fiscal years 2017–2021,” May25, https:// www.jct.gov/publications.html?func=select&id=5.
[48] Victor R. Fuchs, 2019, “Does employment- based health insurance make the US medical care system unfair and ineffici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21(21), 2069– 70,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9.4812.
[49] Leslie Josephs, 2017, “Fed Ex says US roads are so bad it’s burning through tires twice as fast as it did 20years ago,” Quartz, February1, https:// qz.com/900565/fedexsays-us-roads-are -so-bad-its-burning-through-tires-twice-as-fast-as-it-did-20-years-ago/.
[50]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icers, 2018, Summary: NASBO state expenditure report , November15, https:// higherlogicdownload.s3.amazonaws.com/NASBO/9d2d2db1 -c943-4f1b-b750-0fca152d64c2/UploadedImages/Issue%20Briefs%20/2018_State_Expenditure _Report_Summary.pdf.
[51] Arrow, “Uncertainty.”
[52] 作者未明确指代,此处疑为戏语,指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她是一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女先知,但因为抗拒阿波罗而遭到诅咒,其预言不被人相信。——译者注
[53] Robert D. Atkinson and Michael Lind, 2018, Big is beautiful: Debunking the myth of small business , MIT Press.
[54] 此说法来自美国体育界,指某一更高等级球队的预备队,其代表为美国职业棒球小联盟,它依附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并设立各个等级,为年轻球员提供训练和比赛等发展机会,使这些球员为大联盟赛事做好准备。小联盟内的球队一般来说皆为独立经营,但可通过签署标准化的球员发展合约而成为某支大联盟球队的附属球队。这样的联盟形态通常也被称为“农场系统”“农场球队”等。——译者注
[55] Lawrence Lessig, 2015, Republic, lost: version 2.0 , Hachette.
[56] All data from https://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August2019.
[57] Brill, America’s bitter pill .
[58] Lee Drutman, 2015, The business of Ameri ca is lobbying: How corporations became politi cized and politics became more corporat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9] Zack Cooper, Amanda E. Kowalski, Eleanor N. Powell, and Jennifer Wu, 2019,“Politics and health care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23748,revised February.
美国资本主义未能给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带来美好的生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好工作消失不见,实际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这使劳工阶层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这不仅反映在生活水平的降低上,还反映在劳工阶层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对许多人来说,那些提供支持的机制——婚姻、教会和社区——不再发挥作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受到挑战,生活的意义也彻底丧失。正如埃米尔·杜克海姆的理论预言的那样,自杀率已经上升,在当前情况下不仅指蓄意的自我伤害,还包括创造一种环境,使抑郁和药物成瘾泛滥,并由此导致绝望的死亡。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又该如何解决?
我们坚信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力量。在过去250年里,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使那些国家成为当今的富裕国家。在过去50年里,中国和印度等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竞争性的自由企业一直努力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贸易、创新和人员流动是这一叙事的核心积极因素。但是,资本主义真正的神奇之处在于,要确保市场、贸易、创新和移民都是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与人民为敌,或者只是为少数人服务,但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今天,美国的劳动人民往往无法从市场经济中受益。从阿片类药物泛滥到整个医疗行业的怪象,我们已经见证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如果那还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
在许多经济领域,补救措施并不是完全废除市场,而是对其加以改造,使其更像真正自由和竞争的市场,它们本应如此,但现在却越来越走样了。在其他情况下,需要政府代表人民进行干预。然而,政治权力已经越来越远离劳动人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实施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改革。
不平等常常被视为当今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奥巴马总统曾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许多左翼人士认为,我们需要制订新的再分配计划,对富人课以更重的税,并将所得税款转移给穷人和用于生产能够造福所有人的公共产品。不平等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正如我们所见,它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今美国社会恰如传说中罗宾汉理想社会的镜像,在这个社会中,资源确实是在重新分配,但不是像罗宾汉所说的那样,从富人到穷人向下分配,而是从穷人到富人向上分配。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诺丁汉郡治安官式的再分配,我们认为美国医疗制度的许多方面就是如此运作的。一开始,人们可能认为掠夺穷人并不是特别有利可图,因为他们的财富太少了。但穷人巨大的人口数量弥补了他们相对较少的人均资源,同时富人数量有限,因此诺丁汉郡的治安官和他的亲信大可以靠剥削穷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财富向富人的转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劳工阶层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财富的向上再分配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资本主义也不必非要如此运作,尽管这种风险总是存在。不过,美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沦陷,在政府的首肯和纵容下为富人的利益服务。不平等的问题在于,上层社会的财富和收入有太多属于不义之财。换句话说,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我们不会指责那些以利于众人的方式为自己谋取财富之人。
对低工资工人的三大威胁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技能较低的工人面临来自低工资国家移民的竞争。他们还必须与国外的工人竞争,后者生产的商品进口到美国,替代了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并因此而威胁美国工人的工作。除了人类之间的竞争,工人们还越来越必须与机器人竞争,因为机器人已经悄悄地接管了许多原来由人完成的工作。机器人不需要医疗保险或其他福利,也不需要人力资源支持或者不断提升的生活费用。现有的税收制度对购买新机器提供补贴,但不会补贴劳动力成本。我们认为,移民虽然引起了很大关注,但它不可能是劳工阶层工资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也不可能是跻身中产阶级的社会阶梯被打破的主要原因。对美国而言,全球化和自动化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在美国的影响之所以比在其他国家更大,是因为美国特有的种族历史、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荒谬而昂贵的医疗制度。
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开始面对这三大威胁之时,也恰好是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因此,就算人们能够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他们也不能像其父辈那样,或像他们自己预期的那样,迅速改善生活。单单这个因素,就决定了工资增长不可能保持从前的速度。而在增长红利不能平等分配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更容易受增长放缓影响。例如,当每个人都健康幸福时,医疗行业的寻租行为或许还可以忍受,而一旦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对寻租行为的容忍度则会低得多。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之外,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服务业,即使是同等水平的工作,工资也相对较低,同时由于工会的势力较弱,工人相对于雇主的权力也更小。
许多人将工作的消失归咎于移民窃取了工作。不仅美国,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也不乏挥舞民粹主义大旗的政治家,努力挑动着人们对移民政策的恐惧。
我们想首先公布一个免责声明。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属于第一代移民,另一个出生在美国,但她的祖先在19世纪中叶从爱尔兰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并且她的家庭仍然深受本民族和宗教遗产的影响。或许更相关的一点是,我们都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并且都在高等教育行业工作。在这一行业,移民早已司空见惯。在美国,超过2/3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由非美国出生的人获得的,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导致教师队伍中也有超过2/3的人并非在美国出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2/3的教师出生在国外。从职业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种多样性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观点、经验和价值观是创造性互动的基础。话虽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一种担心,即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虽然地理位置是在美国,但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社区更像小联合国。我们也很难通过个人经历想象,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就业市场受到威胁时,他们对移民的感受。
美国的移民来源极其多元化。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与本地人口基本相同,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许多移民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其他许多移民则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 [1] 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例如,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可能会帮助他们的同事变得更有生产力,从而实际上增加后者的收入。移民具有悠久的创新历史。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爱丁堡出生和长大。詹姆斯·卡夫发明了生产奶酪的巴氏杀菌工艺,他是一位加拿大移民。移民发明的产品还包括正电子发射体层仪、电子游戏的桨杆控制器和锂电池。贝宝、特斯拉汽车和Space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是一位移民,谷歌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也是一位移民。 [2] 201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所有6位获奖的美国人都是第一代移民。2015年,我们两人中的一个荣幸地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当年四位获奖的美国人中,有三人是第一代移民,另一位是移民的儿子。很难相信,限制这样的移民者对美国来说是个好主意,尽管人才输出国对此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人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移民,那些人将会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直接竞争,而后者的绝望正是本书的主题。
就在撰写本书内容时(2019年),美国公民中出生在外国的人口比例约为13%,接近一个世纪前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60万人合法移民,到90年代增至80万人。自2001年以来,每年的移民人数超过100万人。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也相当庞大,但近年来,非法移民流入与流出人数相当,因此,估计非法移民的总数稳定在大约1100万人(占记录在案的外国出生人口的25%)。 [3] 如果美国南部边境开放,将会有许多移民来来去去,就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墙阻碍了这种人员往来,把一些墨西哥非法移民困在美国,同时把其他人挡在墙外。 [4] 在今天的美国,外国出生人口增长最快的不是传统的接收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而是一些非传统移民州,其中许多在南部。如果人们对移民过程不熟悉,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中也没有在上一代移民潮中来美国的移民,那么他们对移民的反应,哪怕是数量有限的移民,也可能会更为负面。
富裕的美国人、农民和雇主都喜欢低技能移民。他们喜欢廉价的园丁、农场工人、家务佣人和保姆。他们可能和劳工阶层一样,也认为移民会降低工资,但他们乐得见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尽管这会令劳工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但他们的利润却增加了。雇主经常抱怨缺乏劳动力,如果没有移民,他们可能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工资或增加福利。移民问题的批评者表示,这正是问题所在。 [5] 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工人竞争,就像在国外使用更多廉价工人或更多机器人一样,当然可以降低工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但是,他们是否已经这样做了是问题的关键。
为了对劳工阶层就业市场的崩溃提出合理解释,我们一直在寻找可能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实际工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不断下降的因素。鉴于此,我们在考虑移民和工作时,需要区分近期和远期影响。假设在几个月或几年的短时间内,工作的数量相对固定,那么对于本来就在某地生活的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移民会使当地人口流离失所或工资下降,他们还将提高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失业的工人、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利润为企业家或其他雇主提供了扩张的机会,尽管开设新公司或建造工厂、购买设备供工人使用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资本会根据情况做出调整,经济也会增长。毕竟,历史曾见证了在人口出现巨大增长的情况下,失业率并未长期上涨,实际工资也实现了增长。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下面的情况就根本不会出现,即工作的数量和总体薪资固定不变,如果工人数量增加,一定意味着找到工作的概率减少和所有人的工资下降。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够长,足以使资本适应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因此很难将工资长期下降归因于移民。但是,如果每一波浪潮都紧随着另一波浪潮,经济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充分调整的机会,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工资就可能持续降低,至少直到不再有大规模移民为止。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在其2017年的移民报告中,总结了根据调查得出的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报告写道“特别是在10年或更长的时期内,移民对本地整体工资的影响可能很小,或接近于零” [6] 。针对较短的时期,调查有一系列发现,其中一些显示出移民对工资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前一波移民潮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许多移民不是非技术移民,而是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尽管移民中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多于仅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文凭的人,但同期学士学位的工资溢价仍然大幅增长。无论移民在较短时期内对工资的影响如何或是否与预期相符,我们的判断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口工资长期下降的过程中,移民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远未解决,甚至在学术经济学家中也是如此。
移民并不是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的唯一途径。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需要工作的人。2000年以前,妇女,特别是没有学士学位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大幅提升(见图11-2)。正像移民的收入低于本地人一样,妇女的收入通常低于男性。尽管目前人们仍然在研究就业妇女人口增加是否对男性的工资产生了负面影响(结果尚不确定),这个话题并没有像移民问题那样引发大量争论和愤怒情绪。这使我们认为,此处辩论的焦点不是人数,或者新出现的工人夺走现有工人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工人数量增加导致工资被压低,或移民使人口数量超过国家的容纳能力,尽管最后一点确实是一个值得严肃探讨的话题。移民问题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一定有别的原因,例如,移民与“我们”不同,被视为对“我们的文化”形成威胁。特别是在那些不熟悉移民,但工作岗位因其他原因消失或降级的地方,移民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替罪羊。
我们中的一个人仍然记得自己在印度的一次经历,那是一次乘坐拥挤的火车从艾哈迈达巴德到孟买的经历。十几个人挤在一个车厢隔间,实际上是分为上下两层的长凳,坐满了人。几个小时前,我们还都是陌生人,但到后来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分享食物、水和火车旅行中的趣闻。火车每到一站,都会有新的乘客加入,有些人试图挤进我们的俱乐部,但却遭到无声的敌意。到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只好靠得更近一些,并允许一个陌生人加入。到下一站,陌生人也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准备击退下一轮“移民”。当然,随着火车开过一站又一站,我们所有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舒服。
对许多人来说,贸易和自动化显然是美国工人的敌人。低工资国家的商品蜂拥而至,使许多过去在美国生产同样商品的人丢掉了工作。美国工人正在被取代,而且取代他们的,不仅仅是蒂华纳等地的工人,还有机器和计算机辅助生产过程。墨西哥等国的工人不能抢走快餐店的工作,也不可能帮人们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或在杂货店收银,但自动售货亭能做到这一切。拥有一定技能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能够适应新技术工作的工人获得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而低技能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境遇则正好相反。
这一叙事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把今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和200年前英国的织布工进行比较。当织布工被机器取代时,他们的工资下降,只有在用手摇织布机织布的方式彻底消失之后,工资才停止下降。如果这两种情况确有可比性,那些可以被机器人或其他低工资国家工人取代的工人,都将面临工资下降的情况,并且只有在这些工作彻底消失,或低工资国家的工资水平涨到和美国一样时,这种下降趋势才会停止。到那时,除非工资政策有所改变,否则将有更大一部分美国人不得不从事无法外包的服务性工作,赚取仅能勉强糊口的低工资。当然,有一些服务性工作的报酬相当丰厚。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报道,2017年纽约州水管工的年平均工资为7.8万美元。 [7] 不过,在2018年,如果一个单身人士按照联邦最低工资标准(7.25美元/小时)全职工作,他会发现,自己的工资仅比美国人口普查局给出的贫困线高出1400美元(14500美元和13064美元)。 [8] 这无疑将是一个经济、社会和社区被渐渐摧毁的漫长而惨淡的过程。
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曾与人合著了一系列论文,分析了一些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工人及其社区的影响。 [9] 虽然很难得出准确或毫无争议的数字,但他们估计,由于它们崛起,美国失去了200万至300万个工作岗位;1970—1990年,美国约有1800万个制造业工人,2019年的制造业工人人数约为1200万。这些消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产品已经被进口商品取代的制造业地区,而且造成的影响长期持续,在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失业率不断上升。
在那些受到外国制造的产品冲击的社区中,结婚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与本书的研究结果相互呼应和支持。 [10] 只不过我们更加强调工作长期缓慢的流失和社区的毁灭,而奥特尔和合著者的工作更关注来自外国的进口商品在哪些地区和什么时间出现迅速增长。
全球化不仅导致工作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剧烈动荡。尼古拉斯·布鲁姆及合著者的研究表明, [11] 在美国部分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就业者更为集中,在这些地区,因制造业向国外转移而丢失的工作岗位被新创造的工作填补,包括研发、市场营销,以及管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新工作是由那些裁减制造业工人的公司提供的。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大,美国,也出口了更多的产品,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汽车和半导体出口制造业。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估计,出口创造出200万到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与失去的工作岗位数量相当。但在美国低技能工人更为集中的部分地区,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并没有得到积极的补偿。 [12]
传统上,失业工人的自救路线是从没有工作的一个城市搬到另一座有工作的城市,但近年来,由于那些经济繁荣的城市生活费用高昂,这条迁移路线受到限制。这些高昂的成本可能源于地价高企或其他政策,后者是当地居民出于保护自己和阻止新人进入而推行的。经济繁荣的城市成功地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提升了其工资,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那里并没有立足之地。 [13] 因此,许多失业的工人无处可去,并且如果他们搬家,情况可能更糟。
贸易和创新破坏传统经济的故事非常引人注目,但它同时也极度片面。它还与经济学家对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普遍看法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的观点往往首先提到价格下降的好处,外国制造的商品填满了塔吉特超市和沃尔玛的货架,价格往往是原来商品的零头。我们最近给孙子买了一条10英尺长的鳄鱼毛绒玩具,50年前,在纽约著名的第五大道的玩具店里,这样的东西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但很少有人真的购买。事实上,正是因为更低的商品价格以及它们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才让美国制造商陷入困境。
传统的贸易收益计算方法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从旧有工作岗位向新工作岗位的转变将是迅速而无痛苦的,而且还预期,即使不推出促使这一转变实现的政策,消费者获得的好处也会以某种方式补偿(原有的)生产者遭受的损失。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无疑是好事。二者都能使人类总体上获得更高的收入,因为它们提高了生产力。然而,即使最乐观的评价也承认,贸易和创新既会带来赢家,也会带来输家。当工会比现在更强大时,他们本可以迫使雇主分享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但这些收益在今天已经被资本及其管理者或新技术的运营者独得。著名的底特律条约是汽车行业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共同协议。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鲁瑟同意与通用汽车签订一份长期协议,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可获得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换取不罢工的承诺。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外国激烈竞争破坏了这个协议。由于本土制造的汽车受到廉价进口汽车的挑战,美国汽车制造商为了竞争,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降低成本,例如,将工作转移到国外以降低工资支出,并且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削弱由私营部门提供的社会安全网。这样,全球化导致工会衰落。消费者受益于性能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但汽车工人成为输家。只有当我们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时,这种现象才会是纯粹的好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某些低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不仅如此,高工资和好工作的丧失所冲击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受到其直接影响的社区。相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丧失而言,能够轻松购买巨大的填充鳄鱼毛绒玩具实在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偿。
如果外国公司摧毁了本地工业,但新工作,尽管可能是不同的工作,会在其他地方或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那么美国可以提供相应的福利帮助人们渡过暂时的难关(也许需要好几年),或支付再培训费用。美国有类似的计划,即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保守派政治家,甚至那些强烈支持贸易的人,并不支持这项计划,因此其规模有限。2002年,在讨论旨在对受某贸易法案伤害的人进行援助的措施时,参议员菲尔·格莱姆曾轻蔑地说道:“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努力停止这种行为,而现在我们却在这样做。” [14] 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你正是伤人者。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和暂时性的失业保险在帮助失业工人方面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效果远逊于为其他目的而设计的残疾、医疗和退休福利。即使把所有这些福利加在一起,补偿的效果也极其有限。 [15]
然而,如果没有创新和贸易带来的生产扩张,我们就会失去在总体上更加富裕的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放弃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确保每个人都能从增长中受益。问题不是全球化或创新本身,而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经济学家丹尼·罗德瑞克在1997年写了一本极具先见之明的书,讲述了全球化对富裕国家的影响。这本书的名字叫《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他在书中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否’,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采取明智和富有想象力的行动。” [16] 如果说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是伤害劳工阶层的罪魁祸首,那并不是因为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而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既不明智,也没有想象力。一方面,雇主和公司,在工会缺席的情况下,对保护工人没有什么兴趣,这也许可以理解,因为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股东赚取利润;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并没有竭尽全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位严重,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发生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顾名思义,全球化是全球性的,自动化也是如此。电脑并非只在美国被使用,所有富裕国家都必须应对低成本制造业的崛起。然而,许多富裕国家并没有出现全球化和自动化对工资与就业造成负面影响的局面,也没有绝望的死亡,尽管它们也的确出现了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大萧条以后,英国的实际工资中位数曾持续下降,但在经济大衰退前的20年里,英国的实际工资中位数一直在稳步上升,而在相同时期,美国的工资增长则停滞不前。法国和德国也从外国进口商品,但法国和德国绝望的死亡人数很少。美国发生的一切需要从美国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没有这些挑战,美国劳工阶层的衰落本不会发生,但导致劳工阶层衰落的不是挑战本身,而是如医疗制度这样美国独有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所塑造的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
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之间的一个巨大政策差异是,后者的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网为工人提供保险的力度大于美国。因此,如果就业机会因经济衰退、贸易或技术变革而丧失,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可使失业者免于陷入困境,并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通常是长期工作。同样,对英国和美国的制度进行比较将对我们有所启发。
从1994—1995年到2015—2016年,英美两国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速度均远远低于高工资人群,两国的劳动力市场均越来越有利于高技能人群而不是低技能人群。家庭收入也出现类似的趋势,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及收入最高的家庭。在英国,在收入分配中垫底的10%家庭的税前收入在20年内没有增长,而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最高10%的家庭的税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即在整个时期共增长约1/3。但是,英国家庭的税收及政府福利后收入呈现不同的模式,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家庭税收及福利后收入的增长率基本相同,均为每年增长1.2%。 [17] 在美国,税收和福利的调节作用太小,不会对收入产生影响,税收及福利后收入的图看起来与税收和福利前的图没什么两样:同样是底层人口的收入增长率较低,顶层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反而更高。在这两个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形势均更加困难,但在英国,税收和福利制度弥补了这一差距。
推而广之,那些对贸易更开放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政府,因为与格莱姆参议员不同,他们认为,如果不能阻止劳工阶层的沦落,那么贸易的好处就无法完全体现。与其他富裕国家的工人不同的是,美国工人必须独自面对挑战。
我们并不是说英国的社会安全网是灵丹妙药。英国的脱欧灾难暴露了其社会的巨大分歧,这一点与美国没有太大区别。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绝望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但与美国相比,这个数字依然很小,证明其社会保障网起到了缓冲作用。我们在第十章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国家,收入与死亡之间都没有简单的直接联系。绝望情绪的上升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需要多年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社会保障网的作用是提供保险,由全社会共同分担风险,而不是让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独自承担风险。美国缺乏的,正是这种风险共担的制度,而且就算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也肯定是造成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死于绝望的因素之一。
为什么美国的社会保障网如此薄弱?许多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拥趸,支持“即使身处困境,也不应依赖他人”的观点。美国的种族和移民史也很重要。人们不愿意和他们不认识的陌生人一起参加互助保险计划,并且即使在今天,在非洲裔美国人口占多数的各州,国家一级的福利都尚不普遍,数额也较为有限。 [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而在同期,美国杜鲁门政府推行全国医疗保险的努力因南方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而失败。 [19]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颇具预示性的历史事件 [20] ,美国企业开始承担支付雇员医疗保险的责任,以此规避工资管制。企业最终还为员工提供养老金,形式为由雇主向特定账户存入资金,作为员工的退休后福利。这样一来,美国企业,而不是美国政府,构建了个人社会保障网的主体。这种制度,就像底特律条约一样,在1970年之前运转良好,因为那时医疗费用支出较少,企业几乎不会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德国的进口汽车大量涌入,随后出现更加全面的全球化,再加上医疗费用迅速攀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一制度难以为继。企业无力承担员工的养老金,于是它们通过401(k)自定储蓄计划将责任转嫁到员工身上。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医疗费用的上升降低了现有保险计划的数量和质量。 [21] 然而,即使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保障网中私人出资的比例仍然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富裕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2015年的数据,在美国,私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GDP的9%,而英国和法国分别为4.6%和3.3%。相比之下,法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28%,英国为20.5%,而美国仅为19.8% [22] 。
全球化和来自国外的竞争使得美国公司在为其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方面越来越困难,而机器人则不需要福利。在我们对于工资停滞、福利下降和就业权利减少的叙事中,这些广泛的全球力量构成了基础。但这些力量并非单独起作用,如果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不是远远弱于其他富裕国家,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也会不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其他许多方面的设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不愿意采取将非洲裔美国人也纳入其中的全民保障措施。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此外,近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工人相对于公司的权力下降,不仅体现在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上,还体现在国会的对峙中。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1]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7,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https://doi.org/10.17226/23550. We draw on this compendium of evidence extensively in this section.
[2] Ufuk Akcigit, Salomé Baslandze,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2016,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06(10), 2930–81,http://dx. doi .org/10.1257/aer.20150237.
[3]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
[4] Douglas S. Massey, 2017, “The counterproductive consequences of border enforcement,” Cato Journal , 37(3), https://www.cato.org/cato-journal/fall-2017/counterproductive -consequences-border-enforcement.
[5] Tom Cotton, 2016, “Fix immigration. It’s what voters want,” op-ed,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8.
[6]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 quences , 247.
[7]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d., “How much does a plumber make?,” accessed July 28, 2019, https://money.usnews.com/careers/best-jobs/plumber/salary.
[8] Census Bureau, “Poverty threshold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 .census. gov /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poverty-thresholds.html.
[9] David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e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03(6), 2121–68, http://dx.doi.org/10.1257/aer.103.6.2121. For a later review, see also David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en,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 8, 205–4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041.
[10] David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en, 2017, “When work disappears: Manu-facturing decline and the falling marriage market of men,” NBER Working Paper 23173, Febru-ary, https://www.nber.org/papers/w23173.
[11] Nicholas Bloom, Kyle Handley, André Kurman, and Phillip Luck, 2019, “The impact of Chinese trade on US employmen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apocryphal,” July,https://nbloom. people.stanford.edu/sites/g/files/sbiybj4746/f/bhkl_posted_draft.pdf.
[12] Robert Feenstra, Hong Ma, Akira Sasahara, and Yuan Xu, 2018, “Reconsidering the ‘China shock’ in trade,” VoxEU, January18, https:// voxeu.org/article/reconsideringchina-shock-trade.
[13] David Autor, 2019,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 109, 1–32.
[14] Quoted in Steven Brill, 2018, Tailspin: The people and forces behind Ameri ca’s fifty- year fall — and those fighting to reverse it , Knopf, 181.
[15] Autor, Dorn, and Hansen, “China shock.”
[16] Dani Rodrik,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oc. 178 of 1486, Kindle.
[17] Robert Joyce and Xiaowei Xu, 2019, Inequa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troducing the IFS Dea ton Review ,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May, https://www.ifs.org.uk/inequality/wp-content /uploads/2019/05/The-IFS-Deaton-Review-launch_final.pdf.
[18] Alberto Alesina and Edward Glaeser, 2006,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berto Alesina, Reza Baqir,and William East-erly, 1999,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4(4), 1243–84.
[19] Michael A. McCarthy, 2017, Dismantling solidarity: Capi tal ist politics and American pen sions since the New Deal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1.
[20] 此处似指美国当前医疗保险体系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工资管制。雇主不能提高工资,遂转向通过提供医疗保险等福利吸引人才。——译者注
[21] Jacob S. Hacker, 2008,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arthy, Dismantling solidarity .
[2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参见Jacob S. Hacker, 2019, “The economy is strong, so why do so many Americans still feel at risk?,” New York Times , May 21。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写道:“同业中人,会在一起,即令以娱乐消遣为目的,言谈之下,恐亦不免是对付公众的阴谋,是抬高价格的策划。” [1] 正如我们在医疗行业已经看到的那样,借助市场势力抬高价格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值得警惕。面临不法商人“阴谋”威胁的,并非只有价格,还包括工资。在其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报告了他与杰弗里·苏尔的对话,后者曾在密歇根州沃伦市的圣约翰普罗维登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做护士。该地区的医院希望阻止护士通过跳槽提高薪水,“(医院)高管们经常在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并相互交流薪水的信息”,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娱乐消遣。苏尔作为首席原告参加了一场最终胜诉的集体诉讼,但他的雇主给他找了很多麻烦,以致他被迫辞职,而其他医院也不愿雇用他。他认为这种勾结一直在延续,尽管现在已不再明目张胆。 [2]
克鲁格在讲述他的经历时,面对的听众并不是劳动经济学家或工会会员,而是各国的央行行长,他们正齐聚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出席全球央行行长年会,这证明了各国决策者对越来越壮大的公司可能滥用市场势力的普遍忧虑。人们对商业界一直心存疑虑,担心许多行业集中度上升,商业成为不平等的缔造者,更担心它不能为许多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提供薪资合理的好工作。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忧虑表示认同。虽然我们知道,美国的医疗制度不算成功,至少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相形见绌,但经济的其他方面并没有类似一目了然的证据。商业为消费者和员工带来了巨大而普遍的益处,我们需要在这些益处和其所造成的伤害或存在的任何滥用之间进行权衡。我们的观点是,商业带来的益处是实实在在的,但它造成的损害同样真实可见,有些损害来自合法的企业选择,有些则来自非竞争性行为,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而言,这些损害尤其真切。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像今天一样严重。当时,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经济体,而且和现在一样,经济正在迅速转型。伟大的创新给一些创新型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带来进步的方式,我们没有理由仇视财富,只要它来自造福众生的活动,并且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人得到了公平对待。用经济学的话说,当个人激励与社会激励一致时,个人致富的方式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
不过,这出大戏还有第二幕。赢家很快就会面临来自模仿者和新一代颠覆者的竞争。第一幕中的一些赢家受到鼓舞继续创新,并通过进一步的创新令新进入者望尘莫及,但也有人试图收起身后的梯子,用能找到的所有手段扼杀竞争,以防被他人超越。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从政治家那里获得帮助。在第一幕中,只要有想法并去竞争就已经足够,但在第二幕中,政治保护变得非常有用,有时甚至是必需的。 [3] 在第一次镀金时代,标准石油公司的做法包括收购竞争对手,以及与铁路公司合谋,向竞争对手收取更高的运费,从而迫使其他公司倒闭。古斯塔夫·斯威夫特创建了肉类包装行业,他研究出如何使用冷藏火车车厢和冷藏用冰供应商系统向东部城市输送廉价的新鲜肉类产品。随后,这一行业利用卡特尔和定价协议对付竞争对手。 [4] 此时,个人激励与社会激励不再协调一致,企业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谋求财富。
为大众谋福利的“公众恩人”变成“强盗贵族”,例如,安德鲁·卡内基、安德鲁·梅隆、亨利·克莱·弗里克、约翰·D.洛克菲勒、杰伊·古尔德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西奥多·罗斯福将他们称为“罪恶大富豪”。各州和联邦的政客臣服于这些人,并为他们提供保护。不过,从恩人到恶人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分明。正如经济史学家内奥米·拉莫罗所说, [5] 在当时(正如现在)往往很难判断某些行为到底是好还是坏。公司要扩大规模,可以通过创新(这是好的行为),或通过操控价格(不好的行为)。但是,如何判断公司购买供应商或分销商的行为呢?这些做法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但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竞争。而且,如果对垄断行为投诉的一方是因价格过高而面临出局的竞争者,而后者被淘汰对其他所有人都有利,那么又该如何处理?确定公共利益的平衡点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纸上谈兵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在滚滚政治热浪中实践此事了。
今天的“恩人—恶人”是那些已经变得极其富有的技术创新者,这些创新者和首席执行官、企业主或金融家一起,站在了收入分配的最顶端,他们的年薪高达数百万美元,他们对政治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有些公司,比如谷歌,一开始不愿意参与游说行为,但现在已经成为华盛顿开支最大的游说势力之一。在2006年之前,谷歌基本没有在游说上花什么钱。2018年,它的游说支出高达2100万美元,比任何公司都多。像一个世纪前那样,大众普遍关注的不仅是不平等现象,还关注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即企业如何受到政治力量的保护,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赚取巨额财富,任由工人的生活不断恶化。现在,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未来感到担忧的,已经不限于激进的左派实践家。近年来,针对这一问题涌现了大量专著,其作者不仅包括长期持批评态度的人,还包括昔日的捍卫者、成功的企业家和影响力巨大的前政策制定者。 [6]
第一次镀金时代很快让位于“进步时代”,那个时代通过了许多限制托拉斯和垄断的法律,其中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然而,目前出现了一种怀疑论调,并且在媒体和专业经济学家中引起广泛争议,那就是反垄断法实施不力,使得托拉斯得以在现代重生。反垄断政策及其实施可以而且应该为美国工人和消费者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市场势力滥用的侵害。但我们不能对此期望太高,因为反垄断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竞争的环境,而不是减少因为竞争,或因为华盛顿被金钱力量腐蚀导致的不平等。
今天的新贵很大一部分是新兴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所属的行业在半个世纪前尚不存在。谷歌、苹果、微软、脸书和亚马逊已经取代铁路和钢铁公司,而银行家和金融家则在这两个时代都大发横财。新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时还带来了惊人的改变,这种现象在第一次镀金时代也曾出现。一个世纪前,与朋友和家人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沟通速度非常慢,成本也很高。人们需要奔波数百里听一场难得一听的交响音乐会,或去寻找一本绝版书。今天,我们可以在瞬间找到全球各地的音乐、电影和文学作品。我们坐拥丰富的娱乐和信息,这是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甚至年轻时的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便利。公司为许多美国人提供了很好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薪水丰厚,而且还给人带来尊严和意义。
不过,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并没有分享这些进步的成果。对于低技能人群,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已经变得极其暗淡,因为企业正在积极调整,以应对全球化竞争以及机器人价格下降和能力提升的形势。全球化和自动化最终会为人类带来裨益,但它们也会造成破坏,特别是在短期内,许多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将失去工作。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看到的,打击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并不仅仅是全球化和技术为先的劳动力市场。
过高的医疗保险价格导致企业裁员。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为灾难,其诱因包括寻租行为、受到政治保护的暴利和医疗行业反垄断执法不力。反竞争和寻租行为并不局限于医疗行业。企业合并可以让雇主有权在本地市场设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大公司有可能利用市场势力提高价格。通过压低工资和提高价格,这种反竞争行为伤害了那些不得不支付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和遭受双重伤害的工人。竞争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标志之一,但当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国家蓬勃发展之时,它在美国却逐渐消退。 [7] 不仅在医疗行业,而且在更普遍的商业领域,反竞争行为无论存在于何处,都是向上再分配的动因。
公司通过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攫取财富的手段之一是超额收费。在一个理想(并且只是稍加简化)的世界里,人们要购买某件东西,只需支付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力成本、材料成本和正常利润,不必付出更多费用,也不会有人压制消费者,阻止他们购买负担得起且生产成本低于他们认定价值的产品。按理说,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应该确保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如果某个产品的定价高于其成本,对手就会被潜在的利润吸引并加入竞争,从而推动产品价格下降。如果在位公司拥有垄断权,比如国家授予的独家销售许可,或者对某些关键成分或生产过程拥有控制权,那么竞争将被扼杀,垄断者则可以收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费用。消费者将不得不为较少的价值支付更多金钱,而垄断者的行为不会受到竞争约束。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1984年被分拆前是一家垄断公司,不过它受到的主要指控并非牟取暴利,而是缺乏创新。如今,许多美国人只有一家有线电视公司或宽带提供商可供选择。这些公司是地方性垄断公司,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它们面临竞争。如今,这些地方性垄断企业正受到互联网流媒体的挑战,长期垄断企业往往受到新技术的挑战。比垄断更常见的是寡头垄断,即市场上只有少数卖家,每个卖家对价格都有一定的控制权。某个地区可能只有一家丰田汽车的经销商,但其他品牌汽车的经销商可以提供不完全竞争。苹果并不是唯一的手机生产商,但它有大量忠实的用户,这些用户不太可能转向三星,这使得苹果能够将iPhone的价格定得远远高于其生产成本。航空公司推出常旅客计划,目的就是让旅客在价格上涨时不愿更换航空公司。寡头垄断者有时还会私下或公开串通,以保持高昂的价格。
有许多迹象表明,当前的经济存在缺陷。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销售额来自少数几家大公司,利润率不断上升,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企业合并愈演愈烈,初创企业数量下降。投资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集中度最高的行业。投资是增长的先决条件,它体现了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并提高了生产率,而按历史标准来看,目前生产率的增长相当低。虽然这些大趋势(多数)相互印证,但对于到底应如何解读这些趋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为此感到担心,存在广泛的分歧。
在多数行业中,最大的几家公司所占的销售份额均呈现增加的趋势。例如,在零售行业,销售额最大的四家公司在1980—2015年的份额从15%增加到30%。 [8] 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是大型公司发展最快的行业,这些公司越来越在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零售业的一大巨头是亚马逊公司,而主导航空业的,则是通过合并而成的四大航空公司,即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对竞争的厌恶有目共睹,他喜欢引用彼得·林奇的名言“竞争可能对人类财富造成危害”,他曾长期拒绝投资航空业(“如果一位资本家于20世纪初出现在基蒂霍克,他应该开枪打死奥维尔·莱特”),他还声称对航空公司投资无疑是跳入一个“死亡陷阱” [9] 。但他最近似乎发现,航空业已变得更合自己的口味,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现在是达美航空的第一大股东,以及西南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的第二大股东。 [10] 这种“横向持股”对竞争构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大股东,例如先锋集团,都是被动投资者。 [11] 旅客们对于航空公司间竞争的减少不太可能拥有巴菲特一样的热情。一次从资本的角度有利可图的飞行对乘客而言将是一次不舒服的旅程,乘客们排着队被赶上飞机(有时甚至会被拖离飞机),他们被困在已经变身为高价购物中心的航站楼,登机口在某个遥远的角落。一些航线的机票价格降低了,但也有些航线的机票价格高涨。2019年秋,从纽瓦克出发,到洛杉矶(2800英里)的商务舱往返机票价格是1140美元,到巴黎(3600英里)的机票价格是10000美元,而到香港(8045英里)的价格是7800美元。决定价格的因素显然已经不是服务的边际成本,虽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后者本应是价格的决定因素。
1980年,所有美国公司中有一半的成立时间不足5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3。1980年,这些新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占总就业量的20%,但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0%。 [12] 根据准确测算(尽管准确度要视不易解决的计量标准而定),价格加成(商品销售价与成本价之间的差价)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增加。 [13] 在20世纪60年代,销售利润占售价的平均份额为4%,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份额降为2%,但到2015年,这一份额已经上升到8%。越来越多的公司利润率已经超过销售额的15%。工资在GDP中的占比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大约为2/3,但现在已经下降到60%。 [14]
这些数据可以被解读为美国商业界的竞争越来越弱。借用目前更热门(民粹主义?)的术语,这个制度可被视为越来越青睐商家。卓越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曾表示,垄断利润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平静的生活。 [15] 垄断不仅能带来超高的价格,而且随着恼人的竞争被消除,企业不再有必要改进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或者投资寻找和实施新想法。相反,回报最高的投资不是将利润投资于企业本身,而是投资于挖掘一条护城河,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垄断者可以收购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或投入资金,进行对社会毫无贡献但可为私人带来巨大利益的游说,以保护其市场势力和保证较低的税赋。有证据表明,许多最初号称可以节省成本和降低价格的企业并购,实际上导致了价格上涨,而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表明反垄断监管机构在过去25年一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6]
这些观点能说明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全部。 [17] 大部分加成和利润增长的确是由各行业中的少数公司贡献的,通常是那些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的公司。 [18] 例如,亚马逊大量投资平台建设,航空公司斥资开发网站和用于定价的算法,沃尔玛打造创新的物流、供应和库存管理系统。一旦系统到位,这些公司的生产和交付成本就会下降,利润率则会提升,尽管利润可能要到系统成本付清之后才会增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司的规模相对于同行业中其他公司会有所扩张,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其他一些公司可能发现它们已经无法与之竞争,因此该行业中的公司数量将减少,集中度将上升。成功的创新者很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尤其是在竞争者很少的情况下。在理想情况下,新进入的公司将设法模仿甚至改善市场领导者的机制,随之推动价格下降。当这一过程有效时,技术变革将带来价格的降低和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从而为消费者带来社会效益,尽管这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大批公司出局。 [19]
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集中度并不是因为具有市场主导力量的公司采取了不法行为,而是由于市场从效率较低的公司向效率更高的公司转移。确实,数据表明,利润率的提高并不是各行业典型公司的普遍现象,而只发生在一些赢利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在IT(信息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公司。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这些公司既不是犯罪分子,也不是强盗贵族,而是超级巨星。
行业集中度提高至少部分源于一些公司特别具有创新精神,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公司设置了非生产性市场壁垒。这一说法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因为欧洲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革。在多数欧洲国家,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同样正在下降,资本在GDP中的占比则在上升,尽管英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同样,欧洲企业的利润率也在不断上升, [20] 同时行业集中度不断加剧。所有这些都支持了上面的观点,即导致利润增长的,是超级巨星式的企业,而不是因为美国的游说机制、政治制度或国家特别不愿意强力实施反垄断法。 [21] 近年来,欧洲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加剧,但远没有美国那样严重,这符合一个观点,即贸易和信息技术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美国还存在其他的独特力量,大大加剧了这种现象。
创新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称为熊彼特竞争,这个说法得名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公开宣称自己的三大人生目标——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士、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他后来声称,完全是由于骑兵队的没落,才使他的三大人生目标未能圆满实现,尽管他的这种说辞并不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熊彼特认为,技术进步具有内在的破坏性。拥有新技术的局外人对在位公司构成威胁。对前者而言,将新想法推向市场需要先期投资,并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但如果它们能够取代现有的在位公司,则将有机会获得垄断利润。这可以说是夺取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在市场之中进行竞争。创新是一系列竞赛,是对支配地位的挑战,获胜者将获得丰厚的奖品。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官在他的判决书中深得此点精髓,他写道:“单纯拥有垄断权并收取垄断性价格不仅不违法,而且是自由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短期内,正是由于有机会收取垄断性价格,才会吸引‘精明的商业头脑’入场。它会鼓励人们承担风险,从而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22]
在充斥着熊彼特式竞争的世界里,反垄断监管需要防止成功的挑战者收起他们身后的梯子。暂时拥有竞争优势没有问题,但永远保持优势则不行。监管机构应该对消灭竞争对手的行为进行监管,例如,微软通过在其操作系统中内置自己的浏览器消灭网景,脸书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制药公司收购研发过程中的非专利药物以阻止它们进入市场。行业集中本身不应成为打击目标,因为集中可能代表效率,而不是相反,而且行业往往和市场并不一样。消费者在本地经常会面对单一供应商,例如唯一的有线电视供应商,或者本地机场由单一航空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即使某个行业充分竞争,消费者也可能面临垄断。相反,亚马逊的发展增进了美国许多地区的竞争,特别是在农村和人口稀少的地区,那些地区几乎没什么本地零售商店可供消费者选择。 [23]
市场势力到底有多泛滥是当今经济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同样争论激烈的还有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此表示担心。不过,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垄断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势力是否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实际工资,并因此导致绝望的死亡登场。我们认为,医疗行业无疑存在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行业,例如,航空公司及其所有者的集中度不断提高,或者银行的频繁盘剥行为。我们还担心占优势地位的企业会扼杀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相信,目前还没有任何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商业的竞争程度在下降,并正在通过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24] 的确,对于许多商品和服务来说,创新的浪潮已经到来,从而带来更低的价格,甚至带来许多免费的产品和服务。所有这些创新引发的问题并不是价格过高,而是在于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不仅具有创造性,还具有破坏性。它消灭了以前存在的工作,同时这个进程由于高昂的医疗保险费用而加速,工人在没有强大社会安全网的保护下,被迫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原有工作支持的生活和社区因工作消失而濒于瓦解,并在最坏的情况下,导致绝望和死亡。
正如在只有一个卖方的情况下会产生垄断一样,如果只有一个买家,则将导致买方垄断。此处,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上只有唯一买方的现象。“买方垄断”一词是由经济学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琼·罗宾逊提出的, [25] 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和合作者,也是竞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完全围绕某家公司而生的一座城镇就属于典型的买方垄断例子。与卖方垄断一样,买方垄断中也可能有少数几个雇主,每个雇主都有压低工资的权力,从而构成寡头垄断。买方垄断或买方寡头垄断意味着公司拥有工资制定权,而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工人的工资随行就市,任何压低工资的雇主都会雇不到员工。农村地区是雇主能够支付低于市价工资的典型地方,那里也许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工作,除了快餐店、鸡肉加工厂或国家监狱的工作。农村或小城镇的教师或护士也可能处于类似的地位。工人们当然可以选择搬家,但这样做总是会有成本和风险,找一份新工作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人们可能与自己居住的社区或周围的人存在紧密联系,所有这些都给予雇主压低工资的权力。美国的流动性下降部分是因为许多城市的土地变得非常昂贵,还有部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城市中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买方垄断已经变得日益严重,因而将工资压低到市场竞争水平以下,并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换取更高的利润。 [26]
当劳动力市场处于竞争状态时,如果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工资水平,则雇主将会解雇工人。这是经济学教科书上常见的解释。目前有很多研究都在寻找这样的结论。尽管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以来就没有提高过,但许多州在此期间提高了最低工资,为研究法定最低工资的影响提供了许多机会。迄今为止,最全面和最有说服力的一项研究是由经济学家多鲁克·森吉兹、阿林德拉吉特·杜贝及其合作者共同开展的。他们的研究发现,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没有影响;雇主没有因此解雇工人或减少新员工数量,而只是将工人的工资从略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提高到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 [27]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证据,尤其是英国。英国原来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它在1999年制定了相对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针对英国进行的几十项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一变化对就业产生任何影响。 [28] 如果雇主没有设定工资的权力,上面这些结果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并不像教科书让我们相信的那么强,如果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那么即使被迫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们也毫不意外地将继续雇用工人,因为至少在工资达到某一水平之前,工人创造的价值仍然高于其成本。
在城市工作的人通常比在农村地区做类似工作的人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一个地区的雇主数量很少,那么该地的工资也会低于雇主较多的地区。不过,造成工资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而且就像有关卖方和市场势力的争论一样,如果不了解集中度高或低的根源,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对雇主集中度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做出解释。在国家层面集中度提高的同时,地方层面的雇主集中度降低,这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现象。 [29] 话虽如此,企业的不当行为确实存在。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护士工资的案例表明,几家医院合谋压低工资。当市场上只有少数雇主的情况下,共谋会更容易,而且看上去医院似乎非常善于对病人和雇员两头压榨。 [30] 压低护士的工资会导致人员短缺,医院会通过从合同制劳务派遣公司那里雇用护士弥补这种短缺,尽管从劳务派遣公司雇用护士的成本高于聘用合同护士,但这种聘用方式使医院无须向较大数量的在编护士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也再次证明,有些公司确实会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
雇主经常会让雇员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包括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也会如此操作。虽然此类协议在这些州并不具有效力,但它也可能成为有效的威胁。这些协议限制了员工为其他公司工作的机会,也使雇主更容易压低工资。25%的美国就业者签署了某种形式的竞业禁止条款。 [31] 如果员工掌握了商业秘密或对其他对竞争对手有用的知识(如设计图或程序代码),签署竞业禁止条款自然可以理解,但在低薪工作中并不存在此类理由。然而,在工资水平位于中位数以下的员工中,20%的人在签署了竞业禁止条款的情况下工作。对此情况,(相当)乐观的一种解释可能是,员工在签署协议时清楚这些条款的内容,并因此得到了补偿。但更可能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这一点,而是无意中给了雇主压低工资的权力。
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看到的,公司已经普遍将大量支持性服务岗位外包,如清洁、安保、餐饮服务和运输类工作岗位。这使得公司能够专注于自己更擅长的核心业务,但是外包公司往往是不那么吸引人的工作场所,那里福利更差,工资更低,员工权利更少,晋升的机会很少或根本没有。 [32] 经济学家戴维·多恩、约翰内斯·施密德和詹姆斯·斯普利策写道:“国内的人员外包服务已经彻底改变大量工作的雇佣关系性质,从清洁和安保等相对低技能的工作到人力资源和会计等高技能的工作。” [33] 他们估计,2015年,大约25%从事清洁和安保工作的工人是商业服务公司的雇员;商业服务公司雇用的工人数量是1950年的4倍多。2019年3月,谷歌的临时工和承包商数量已经超过其员工总数,尽管前者与后者并肩工作,有时还做着类似的工作。 [34] 外包业务的增长及其工作等级的降低在破坏劳工阶层的生活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果工会的力量更强大,它肯定会代表会员就公司推行这些做法进行集体谈判。工会的存在可以是(或者它们过去曾经是)对管理层的一种反制力量,能够在企业于工资和公司利润之间进行分配增值收益时,推动企业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以及增加员工福利和限制管理层的权力。2019年初,10.5%的工人加入工会,而在开始有现代数据的1983年,这一比例为20.1%。私营部门更是只有6.4%的工人加入工会。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工会的鼎盛时期,1/3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工会会员。 [35]
由于工会势力被削弱,其在华盛顿的游说声音完全被企业游说淹没,这也是尽管70%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在每小时7.25美元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许多州已经提高其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有29个州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联邦最低工资,从伊利诺伊州的8.25美元到华盛顿州的12美元不等。因此,根据各州的工人数量计算,2007—2016年,实际最低工资增长了10.8%)。 [36]
随着工会的力量逐渐被削弱,公司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管理层摒弃了原来的经营模式,不再坚持既为股东服务,又为员工、客户和社区服务,转而只关注股东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有一点或许令人感到惊讶,那就是人们对于公司的宗旨到底是什么依然存在争议。 [37] 董事会到底该对谁负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董事会只需要对股东负责,但对此也有其他看法,如董事会应对公司本身,或包括消费者和雇员在内的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各个州对此也有相关的法规,而且它们各自的法规也不尽相同,例如,加州就要求董事会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尽管质疑之声越来越大,但公司致力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已成为近年来的主流做法。当然,股东并不直接管理公司,但近年来流行将股票和股票期权作为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一部分,这就使得管理层自身的财富与公司的市场价值紧密相连,因而管理层越来越有动力维护股东的利益。所谓公司的市场价值,是指股东期望公司未来可产生的利润价值,因此,如果管理层的行为会令其他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员工、客户,还是社区)获益,除非这样做会给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否则他们的个人利益将遭受损失。
此外,公司可能面临突袭者的恶意收购,这种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只关注利润的做法。如果一个资金充足的外部人士认为公司的利润表现不佳,作为突袭者,他可以收购足够多的股票,迫使公司改变政策,或解雇管理层,甚至可能为了公司的资产价值而肢解公司。在当今世界,此类突袭变得更容易和更便宜,因为很多股票的持有方都是被动投资者(此类投资者不会试图影响董事会),例如先锋或贝莱德,所以突袭者可以通过拥有一小部分股票获得公司的控制权。
许多人认为,股市的价值是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他们追踪道琼斯指数或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像追踪棒球得分一样,在其上涨时欢欣鼓舞,在其下跌时悲痛欲绝。诚然,未来更好的增长前景通常会提振市场,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一桩,但如果工资下降或管理层用更便宜的机器人取代工人,市场也会上涨。显然,股票市场会对从劳动力向资本的再分配给予积极响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管理层越来越有动力促进这种再分配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很少讨论另一个群体,即那些通过401(k)计划持股的股东,或者任何拥有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的人。从前,员工更有可能拥有固定收益的养老金计划,这些养老金计划的资金是由其他人负责提供的。股票市场的价值可能与投资者有关,但与广大雇员无关。那些拥有固定缴款计划或者投资于股票市场的雇员则会因市场的良好表现而直接获益,因此当工资下降或工人被自动化机器取代时,他们也会得到好处。持有这些投资资产的主要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表现良好。因此,通过以固定缴款的养老金计划取代固定收益的养老金计划,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为成功的美国人又通过损害受教育程度较低同胞的利益而获利。我们在此并不是暗示,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正在主动与劳工阶层为敌,但他们的默许无疑为自己谋得了丰厚的报酬。自1990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年上涨逾7%。
美国拥有许多规模巨大且利润丰厚的公司以及大量超级富豪,这种状况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两者对政治施加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这会让我们面临下面的风险,即财大气粗者能够更有效地参与美国政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人则无缘参政议政,正是后者的死亡,构成了本书的主题。穷人成为富人利益的牺牲品,并且无人为他们的利益发声。今日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失灵,而对此华盛顿盛行的金钱政治难逃干系。 [38]
2018年,华盛顿共有11654个注册的游说团体,其游说活动共耗资34.6亿美元。 [39] 这意味着,535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平均每人对应了22个说客,或650万美元的游说资金。这笔资金还不包括用作竞选资金的外部资金,后者在2018年达到13亿美元。这些数字很大,也对华盛顿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相对于企业预算的规模来说,它们只是九牛一毛,例如,2015年,汽车制造商在广告上的花费高达470亿美元。 [40]
华盛顿一直不缺少游说者,他们试图说服政府代表其利益行事,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监管改革实行之后,企业才开始以更大的力度进行游说。1971年,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刘易斯·鲍威尔在一份现在非常著名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经济体系正受到广泛攻击”,商界必须培养政治力量,并“积极果断地”使用这些力量, [41] 这一建议在随后的几年中被广泛遵循。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代表商业利益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的团体,并不会代表某一家公司,而是会代表行业协会,这些协会体现了某个行业的集体利益,过去经常(现在也依然)有效地为其成员,如医生或房地产经纪人谋求特别优待。
多数公司没有在华盛顿安插说客,不过,那些安插了说客的公司往往是大公司。2018年,按金额排名,游说支出最高的是Alphabet(谷歌母公司),其次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波音、康卡斯特、亚马逊、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和脸书(1260万美元)。行业协会的手笔更大,按金额排名,游说支出最大的为美国商会(9480万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以及制药厂商、医院、保险公司和医生的行业协会,美国医学协会在2018年的支出与Alphabet差不多。在游说支出金额最高的20个团体中,唯一的非商业团体是开放社会政策中心,这个中心得到乔治·索罗斯的赞助,针对国家安全、民权和移民等问题开展游说活动。医疗行业作为整体(包括制药业、医院、保险公司和医生)在2018年的游说支出超过5亿美元,金融业的支出与此大致相当。劳工团体的总体游说支出仅有4700万美元,不到两者中任意一个的10%。 [42] 正如在企业内部的情况一样,劳工阶层在华盛顿的力量相对于公司,尤其是大公司而言,也已经落了下风。
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游说制度并不是一部强大的机器,财大气粗的公司和个人可以通过游说编写自己想要的立法,然后买通参议员和众议员,使这些法案获得通过。这是因为面对重大政策问题,各方力量竞争激烈,并且会存在多个游说团体同时行动的情况。游说的确很重要,但它并不能操纵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其只为付钱的人说话。不过,它的所作所为吸收了华盛顿的能量,使那些不能或不愿进行游说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一些曾经强大的组织,如工会,其声音已经被淹没。如果负担不起游说,那么你在政治角力中就没有代表,更糟糕的是,用在华盛顿经常被引用的一个贴切说法,如果餐桌旁没有你的座位,那么你就有可能出现在菜单上。
正是在劳工阶层鲜有代表的华盛顿的“餐桌”旁,向上再分配的制度被设计了出来并得到落实。普通人的利益被从餐桌边推开,让位给公司关注的内容。众议员和参议员本应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但却只是全力支持他们所代表的富人的利益,对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则漠然置之。 [43] 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许多劳工阶层关心的问题(例如,最低工资)根本就得不到付诸表决的机会。显然,这种附带游说的民主已经成为一种选择性民主。
在第十三章,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疗费用高昂且不断上升所致。雇主必须支付的其他强制性福利,如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计划、失业保险和工伤赔偿保险等,也有同样的效果,尽管其影响力度较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福利长期以来都是工会努力争取的目标,而一旦它们成为法律,加入工会就不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与劳动力相关的成本还促使雇主将部分工作外包,以减少直接雇员的数量,因为这样做更有利可图。
工人们正在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虽然他们也分享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带来的好处,但他们出售劳动力的市场却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制造业的衰落,借助贸易被外国工人有效取代的威胁,以及私营部门工会的衰落,都降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就业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44] 这与商业游说行为的兴起剥夺了劳工阶层在华盛顿的议价能力如出一辙。许多雇主对低技能雇员的工资至少具备一定的市场势力,并经常利用这种市场势力将工资压低到竞争市场的正常水平以下。外包制的出现消灭了好工作及其附带的良好福利,将这些工作变成几乎没有任何福利的临时性工作。 [45] 对于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再也无缘加入一家令人羡慕的企业,作为其雇员为公众和股东服务,并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意义。
与半个世纪前的先辈相比,今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生活在一个更加险恶的世界里。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其他富裕国家。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也在不断恶化,它们也经历了制造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和工会化程度的降低。但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并不像美国这样昂贵,并且拥有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像美国这样长期停滞不前。所有这些,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绝望的死亡的流行病没有在所有富裕国家蔓延。然而,对于所有国家的低技能工人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阴云密布,这是一个真正值得忧虑的问题。
[1]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 bk. 1.
[2] Alan B. Krueger, 2018, “Reflections on dwindling worker bargaining power and monetary policy,” luncheon address at the Jackson Hole Economic Symposium, August 24, https://www .kansascityfed.org/~/media/files/publicat/sympos/2018/papersandhandouts/824180824kruegerremarks.pdf?la=en.
[3] Luigi Zingales, 2017, “Towards a politi cal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1(3), 113–30.
[4] Naomi Lamoreaux, 2019, “The problem of bigness: From Standard Oil to Goog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3(3), 94–117.
[5] Lamoreaux.
[6] Joseph Stiglitz, 2019,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 Norton; Thomas Philippon, 2019,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 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ghuram Rajan, 2019, The third pillar: 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 Penguin; Paul Collier,2018,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Facing the new anx ieties, Harper; Jonathan Tepper and Denise Hearn, 2018, The myth of competition: Monopolies and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Wiley; Steven Pearlstein, 2018, Can American capitalism survive? Why greed is not good,opportunity not equal, and fairness won’t make us poorer, St. Martin’s; Tim Wu, 2018,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Elizabeth Anderson, 2017,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an Baker, 2016, Rigged: How globalizationand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economy were structured to make the rich richer,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Tim Carney, 2019, Alienated Ameri ca: Why someplaces thrive while others collapse, Harper; Lane Kenworthy, 2019, 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an unapologetic defense, see Tyler Cowen, 2019,Big business: A love letter to an American anti- hero, St. Martin’s.
[7] Philippon, Great reversal .
[8]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and John van Reenen, 2019,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NBER Working Paper 23396, revised May2, figure4, https:// economics.mit.edu/files/12979.
[9] Buffett quoted in Tepper and Hearn, Myth of competition , 2, 198.
[10] Numbers from CNN Business online, February 19, 2019: for United, see https://money.cnn.com/quote/shareholders/shareholders.html?symb=UAL&subView=instituti onal; for Delta, see https://money.cnn.com/quote/shareholders/shareholders.html?symb=DAL&subView=institutional; for Southwest, https://money.cnn.com/quote/shareholders/shareholders.html?symb=LUV&subView=institutional; for American, https://money.cnn.com/quote/shareholders/shareholders.html?symb=AAL&subView=institutional.
[11] Einar Elhauge, 2019, “How horizontal shareholding harms our economy — and why anti-trust law can fix it,” SSRN, revised August4, http:// dx.doi.org/10.2139/ssrn.3293822; José Azar, Martin C. Schmalz, and Isabel Tecu, 2018,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Journal of Finance , 73(4), 1513–65.
[12] Tepper and Hearn, Myth of competition .
[13] Susanto Basu, 2019, “Are price- cost markups r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discussion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3(3), 3–22; Chad Syverson, 2019, “Macroeconom-ics and market power: Context, implications, and open ques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 tives , 33(3), 23–43.
[14] Jan De Loecker, Jan Eeckhout, and Gabriel Unger, 2018,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November22, http:// www.janeeckhout.com/wp-content /uploads/RMP.pdf.
[15] John R. Hicks, 1935, “Annual survey of economic theory: The theory of monopoly,”Econometrica , 3(1), 1–20.
[16] Carl Shapiro, 2019, “Protecting competi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Merger control, tech titan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3(3), 69–93.
[17] Carl Shapiro, 2018, “Antitrust in a time of pop u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61, 714–48.
[18] De Loecker et al., “Rise of market power.”
[19] John Van Reenen, 2018, “Increa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firms: Market power and the market economy,” prepared for the Jackson Hole conference, https:// www.kansascityfed . org /~/media/files/publicat/sympos/2018/papersandhandouts/jh%20 john%20van%20 reenen%20version%2020.pdf?la=en.
[20] Autor et al.,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a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The Labor share in G20 economies ,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20 Employment Working Group, Antalya,Turkey, February 26–27, https:// www.oecd.org/g20/topics/employment-and-social-policy/The-Labour-Share-in-G20 -Economies.pdf.
[21] For a contrary view, see Philippon, Great reversal .
[22]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540 U.S.398 (2004),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02-682.ZO.html.
[23] Esteban Rossi- Hansberg, Pierre- Daniel Sarte, and Nicholas Trachter, 2018, “Diverging trends in national and local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5066,September.
[24] For an argument to the contrary, see Philippon, Great reversal .
[25] Joan Robinson,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Macmillan.
[26] David G. Blanchflower, 2019, Not working: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jobs go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vid Autor, 2019,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 109, 1–32.
[27] Doruk Cengiz, Arindrajit Dube, Attila Lindner, and Ben Zipperer, 2019,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 wage job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3),1405–54.
[28] David Metcalf, 2008, “Why has the British national minimum wage had little or no impact on employment?,”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50(3), 489–512; David Card and Alan B. Krueger, 2017, “Myth and measurement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bor economics,” ILR Review , 70(3), 826–31.
[29] Kevin Rinz, 2018,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earnings mobility,” US Census Bureau, CARRA Working Paper 2018-10, September,https://www. census .gov /content/dam/Census/library/working-papers/2018/adrm/carrawp-2018-10.pdf.
[30] Krueger, “Reflections.”
[31] Krueger.
[32] David Weil, 2014,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3] David Dorn, Johannes Schmieder, and James R. Spletzer, 2018, “Domestic outsour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31, 1, https:// www.dol.gov/sites/dolgov/files/OASP/legacy/files /Domestic-Outsourcing-in-the-United-States.pdf.
[34] New York Times , 2019, “Senators urge Google to give temporary workers fulltime status,” August 5.
[35] Henry Farber, David Herbst, Ilyana Kuziemko, and Suresh Naidu, 2018, “Unions and inequality over the 20th century: New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24587, May, https://www.nber.org/papers/w24587.
[36] Kathryn Abraham and Melissa Kearney, 2018,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the US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io: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24333,February, https://www.nber.org/papers/w24333.
[37] 我们衷心感谢奥利弗·哈特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讨论。
[38] The following draws on Lee Drutman, 2015, The business of Ameri ca is lobbying: How corporations became politicized and politics became more corpor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2011, Winner- take- 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 Simonand Schuster; and Brink Lindsey and Steven M. Teles, 2017, The captured economy: How the powerful enrich themselves, slow down growth, and increase inequa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 Data from https://www . opensecrets. org, accessed August 5, 2019.
[40] Stephanie Hernandez McGavin, 2016, “Volkswagen Group leads automotive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Automotive News , December9, https:// www.autonews.com/article/20161209 /RETAIL03/161209824/volkswagen-group-leads-automotive-spendingon-advertising.
[41] Lewis F. Powell Jr., 1971, “Attack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system,”confidential memo-randum to Eugene B. Sydnor Jr., August 23, Supreme Court History:Law, Power, and Personality, PBS, accessed August14, 2019, https:// web.archive.org/web/20120104052451 /http://www.pbs.org/wnet/supremecourt/personality/sources_document13html..
[42] Data from https://www . opensecrets. org, accessed August 5, 2019.
[43] Martin Gilens, 2014,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 - cal power in Ameri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rry M. Bartels,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 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4] Dani Rodrik,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Weil, Fissured workplace .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公平的美国。问题是,不同的人对什么是公平有着迥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但是,我们在有些方面仍然大有可为,例如,重点关注那些明显的不公之处,即多数人一致认为错误的社会特征。我们不必就公平的所有方面都达成共识再要求进行改革。这就是经济学家兼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所称的比较方法,他将之与以描述理想社会为开端的先验方法进行了对比。 [1] 如果我们能够明确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并就此达成共识,那么每解决一个问题,都将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以一些具体问题为例,人们普遍认为,从人类的苦难中获利是错误的,因而这种苦难导致的不平等有失公平。此外,无论右派还是左派,即使政治观点迥异,人们也普遍认为,寻租和裙带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此外,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对财富的追求,我们都同意,凭借特别优待谋取财富,例如,做出亚当·斯密谴责的所谓支持“荒谬和压迫性垄断”的行为,也是不公平的。与此相反的是,当前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认为任何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行为都理所当然是可取之举。
许多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支持如下观点:人们拥有的越多,在制定政策时,对福祉赋予的权重(优先权)就应该越小。这种观点首先在经济学上得到广泛应用, [2] 现在被哲学家称为“优先主义” [3] 。优先主义者支持平等,在经济上,优先主义者在设计税收制度时追求实现收入平等,但同时认识到下列事实导致的局限性,那就是人们的税赋越重,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就越小。因此,最终的税收制度取决于现实性问题,特别是人们对税收的反应以及富人对其他人的福祉有多大贡献。同时,税收制度还取决于价值观,特别是优先主义,尽管并非人人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按我们的推测,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赞同优先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鼓吹这种观点在道德层面存在争议,就像优先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向占据收入分配顶层的前1%的人口再分配额外的收入,对社会的价值如此之小,所以可以忽略不做。 [4]
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理应享有优先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处于困境中的人在收入或财富方面的优先权有所下降。与绝望的死亡相关的痛苦是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将顶级富豪的财富以再分配的手段转移给普通的有钱人,甚至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并借此减少不平等,在我们看来,除非它还能够带来其他好处,否则这种做法似乎意义不大。这就是我们并未纠结于不平等现象本身,而是更关注导致不平等现象出现的部分原因,如通过盗窃和寻租,或通过我们在本书中描述的非自愿的向上再分配。确切地说,我们并不否认,不平等有时会导致其他重要的社会目标受到损害,例如,富人有可能会利用其财富侵蚀民主制度,或破坏大多数人依赖的公共产品。但是,我们反对按照优先主义理论计算得出的针对最高收入者的高边际税率。相反,我们更建议应该对寻租行为予以直接打击,如果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必将大大减少不平等现象。
药物过量使用致死是人数最多的一类绝望的死亡。作为一个更大规模流行病的一部分(这个流行病还包括酗酒和自杀导致的死亡),它反映了我们在本书中描述的社会失灵。然而,医药公司的行为就好比在阴燃的绝望上浇上汽油,导致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阻止毒品流行并不能消除绝望的死亡的根源,但它无疑能够拯救许多生命,因而应成为当务之急。
一旦成瘾,想要治愈将极其困难,即使成瘾者全力配合,也很难。人们普遍认为药物辅助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治疗,这通常是因为费用问题。有报道称,一些地方的药物过量使用致死人数大幅减少,其中就包括俄亥俄州代顿市,在约翰·卡西奇州长的领导下,俄亥俄在全州范围扩大了医疗补助计划,同时警察和公共卫生官员共同致力于治疗而不是维持治安。 [5] 无论是针对药物过量使用问题,还是针对其他医疗问题,进一步扩大医疗补助计划都将有所帮助。
今天,医生对阿片类药物处方的危险性更加了解,远远超过大流行的初期,阿片类药物的处方率也已经在2012年见顶。不过,截至2017年,每100个美国人仍然对应58张阿片类药物处方,是1999年的三倍,同时每张处方的平均药物用量为18天。 [6] 如我们所见,20年来阿片类药物处方的膨胀并没有减少疼痛症状的报告。尽管我们对饱受疼痛折磨的人们深感同情,但我们仍然相信,在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过程中,存在处方过度现象。医疗制度需要探索更好的选择,包括1999年以前使用的各种替代疗法。保险公司也应该为这些治疗付费,即使它们比滥开止痛药的费用更高。
今天,美国的医药行业已经功能失调,同样失灵的还包括整体医疗制度。奥施康定本不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大规模向人群提供成瘾性药物可能导致的后果。作为更广泛的医疗改革的一部分,美国需要设立像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那样的监管机构,评估各种治疗方法的益处和费用,并有权阻止那些效益不佳的治疗方法投入使用。当然,这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例子。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医药市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一般而言,自由市场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的观点不可辩驳,但这并不适用于医疗制度。 [7] 不受监管的医疗市场对社会没有好处,受监管的市场反而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在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似乎成功顶住了政治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导致其被关闭或者将其变成吸引寻租者的磁铁。 [8] 在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和控制医疗费用方面,美国应该效仿其他富裕国家,提供全民医保极其重要,而控制医疗费用更加重要。美国目前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是最糟糕的,政府的干预不但未能控制医疗费用,反而为寻租创造了机会,并因此而抬高了费用。不受监管的医疗市场不可能提供社会可接受的覆盖范围。正如肯尼斯·阿罗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在医药领域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完全不可容忍” [9] 。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同样必需的还包括对无力支付费用的人提供补贴。如果不考虑这些方面,任何改革都注定会失败。
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至少从原则上讲,更好的医疗制度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由于当前美国的医疗制度浪费严重,因此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更高效的体系,既可以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又能够节省大量金钱,还能够提高获取医疗服务的公平性。这样的系统不仅可以覆盖目前没有医疗保险的2850万美国人(截至2017年), [10] 而且还可以增加普通就业者实际到手的工资。许多工会拥趸和政界人士之所以对取消现行医疗制度心存疑虑,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多年来收入非但一直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因而人们担心,取消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将是对这些工人的进一步打击。但是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这一问题,看到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正是导致工资增长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危言耸听者经常高喊,美国负担不起全民医疗保险,如果由政府买单,则将在无限期的未来需要巨额的额外税收,但这未必是事实。我们知道,这个听起来像乌托邦梦想的事情远非乌托邦,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做到这一点。但实现目标绝非易事也的确是一个事实。为了改善今天医疗保障方面的混乱状况,我们需要做大量工作,这与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全新体系大不相同。即便如此,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成功可以带来的巨大益处,并且在设定清晰目标的同时,也要充满激情。
任何可行的医疗改革方案要想顺利实施,都必须具有强制性,以防止那些不需要保险的人拒绝支付费用,同时必须控制成本,以免服务提供商的收入受到挤压,因为不是所有的提供商都资金雄厚。新的方案还将削减一些目前拥有医保的人可以享受并非常喜欢的产品或治疗。没有人喜欢被强迫,尤以美国人为甚,他们厌恶医疗服务需要定量配给的想法,但是显然他们并不反感根据钱多钱少确定医疗服务的配额,并将那些没有钱的人完全排除在外的主张。他们还希望得到相互矛盾的结果,例如,一方面希望医疗保险能够覆盖既往病史,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没有既往病史的情况下不必购买保险。我们花在医疗上的每一分钱都会成为某人的收入,而那些人会为维持现状而拼命抵抗。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人之所以努力抗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收入,而不是为了大众的健康,或者为了传说中的自由市场医疗制度,后者是医药公司在面临价格管制威胁时最喜欢唱的高调。
对目前正在讨论的几个方案,我们并不支持其中任何一个。目前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同做法,这些做法本身就因国而异。有些说法并不正确,例如,说除了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英国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支付医生和医院的费用。除了那些费用极其高昂的计划,如由联邦政府向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即面向65岁以下的人开放这项计划,并由税收承担全部费用,我们还有很多选择。有些国家与规模较小、监管严格的保险业和私营保险公司合作,但它们都通过某种机制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参保,并保证对一些人提供补贴和严格控制成本。 [11] 当然,在其他国家有效的做法可能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收入不同,并拥有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期望。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毕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思考医疗制度问题,他写道:“美国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但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历史和环境的制度。” [12] 他已经设计一个详细的计划,该计划使用代金券,并且不是单一付款人体系。 [13] 这个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类似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的成本控制委员会,并且通过专门的增值税提供所需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计划,重点在于延伸医疗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但并不立即将全部费用转嫁给政府, [14] 而是要求雇主继续提供医疗保险,或者在不提供的情况下,向一个联邦计划供款。
几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政府在新的医改方案推出时必然会增加支出,但应在长期内控制费用的增长,这样可以确保医疗服务提供商的收入不会突然减少,而是缓慢地将其利润降到较低水平。医疗业游说团体是华盛顿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进行改革时如果不能给他们好处,那么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推行。如果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受他们剥削,而一个精心设计的改革,加上费用控制,将通过对那些日益昂贵而收效甚微的治疗手段进行严格控制,慢慢减少我们不得不向他们缴纳的贡金。我们希望再次强调,虽然设计一个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并为其筹措资金会涉及许多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包括需要寻找大量凭空产生的资金支持一个全新的福利计划。现有医疗制度耗费的资金已经远超所需。因此,目前的挑战部分在技术和金融工程方面,需要找到重新分配资金的方法,另一部分在政治工程方面,需要通过给予当前的受益方充足的好处,以换取它们对推动改革进程的支持,并在长期内逐步收回这些好处。1946年,时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的奈·贝文在推出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时,被问及他是如何应对医生游说团体的(后者将他比作纳粹医疗元首)。他的回答是,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用金子堵住了他们的嘴” [15] 。
工会的衰落使权力从雇员手中转移到经理和资本所有者手中。尽管我们希望看到工会会员不断减少的趋势得到逆转,或者至少能看到工会像过去一样发挥作用,但我们认为,工会重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使它最终能够重生,这一进程也很可能非常缓慢。
美国公司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也不大,像欧洲许多地区那样,在公司董事会中设立员工代表的做法同样不太可能。一种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但仍然有效的改革将是对企业现在所从事的某些有害做法加以严格监管。例如,应该有可能确保外包公司的存在不能仅仅是为了削减福利或利用非法移民压低工资。竞业禁止条款也应被全面禁止,就像加州目前已经做到的那样。
尽管税前收入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但欧洲的社会保障网多年来一直足够强大,从而得以防止实得收入的差距加大。 [16]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例子,近年来,英国的社会安全网有效发挥作用,抵消了收入最高人口的收入也增长更快的影响。话虽如此,我们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绝望的死亡与缺乏社会安全网有关,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不同国家之间。尤其需要看到,处于这场绝望的死亡流行病中心的,是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女,而他们远不是美国最贫困的群体。我们已经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以及经济大衰退期间,无论是他们的贫困状况,还是他们的收入变化,都没有和死亡率之间产生任何明显的联系。
如果我们令时光倒流40年,在全球化和自动化导致人们失去工作和收入时,如果拥有一个更健全的社会安全网,无疑能使他们在度过这一转型期时不会那么痛苦。全民医疗保险也拥有同样的功效。同时,不附带条件的福利还将缓解工资下降的压力,因为那会让人们不必那么急切地在短期找到新工作,并且全民医疗保险将降低企业解雇工人的动力。现有的一些福利是附带条件的,例如“所得税抵免”只有在有工作的条件下才能享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青睐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则将有助于阻止工人流出劳动力市场。
然而,不过分依赖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将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沿用迈克尔·杨对“民粹主义者”和“伪善主义者”的划分,并以受教育程度划分美国人口和欧洲人口,那么社会安全网就好比一个创可贴,虽然有用,但却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建议。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为,我们需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而不能局限于那些通过精英制度考试的人,但至少对于我们二人而言,这一点如何做到尚不清楚。 [17]
普遍基本收入 [18] 的概念有很多拥护者,的确,在一个机器人已取代许多乃至大多数工人的世界里,通过类似政策确保国民收入不会全部归于机器人的拥有者和发明者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距离实现这一反乌托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即使现在也存在强大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持普遍基本收入的观点,正如存在支持全民医保和全民教育的论据一样。自由社会的人应该免费拥有一定的基本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我们特别推荐菲利普·范·帕里斯和扬尼克·范德堡特雄辩的论点。 [19] 他们指出,普遍基本收入将增进每个人的自由。许多人认为,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将有助于政治和民主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没有它则会使政治和民主彻底失效,尤其是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地方。 [20] 此外,还有一个有关富裕国家收入来源的强有力伦理论据,即尽管这些国家的收入与当前的努力分不开,但其在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遗产的支持,如教育和就业基础设施,以及我们欠上一代人的物质和社会资本。 [21] 全社会每个人都应有权分享这些继承的财富。
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支持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从算术角度来看,这一概念在左右两边经常被引用的支持作用将相互抵消。在其右边,这项福利取代了所有其他政府转移支付,包括养老金和伤残补助金,因此许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境况将比现在恶化。在其左边,普遍基本收入被视为对现行制度的补充,这使得它非常昂贵,每人每年一万美元的普遍福利意味着目前的税收将大概翻番。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更现实的可能性,即可以通过修改现行福利和税收政策,使其更接近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例如,通过对福利制度加以改进,使穷人不会因任何额外收入而面临高额税收。但事实证明,就连这一点也很难以可行的成本加以实现。 [22]
普遍基本收入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工作。它的捍卫者分为两类,一类人想证明普遍基本收入不会降低人们工作的意愿,另一类人则认为不工作的自由是一种特性,而不是一种缺陷。毫无疑问,对于许多纳税人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为他人的医疗或他人子女的教育买单感到不满,现在要让他们为别人的闲暇买单,这无疑是一种过分的要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描绘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勤勉牙医,他每天开车在雪地中奔波,治疗脾气暴躁的病人,而这些病人则喋喋不休地抱怨他收费太高,根本没人关心他已经累得患上静脉曲张,然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一群成年人靠着他们的普遍基本收入整日无所事事,阅读诗歌和借助艺术陶冶情操。 [23] 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充分参与生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普遍基本收入政策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意愿,减轻了他们寻找有报酬工作的压力,那么实际上是在减少他们的生活机会。这使得普遍基本收入的政治可行性取决于它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普遍基本收入有可能为失去工作的人提供自由,使他们得以为获得新工作接受培训,开展新的活动,为社区做出贡献,更充分地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并且从长远来看,重建自己的生活。尽管我们十分关心那些饱受绝望的死亡威胁,以及因失业而丧失生活意义和地位的人,但我们很难将普遍基本收入政策视为改革的最佳途径。
反垄断执法是当今经济学和法学界极具争议的话题。一方认为,行业集中度、市场势力和剥削行为不断加剧,而与此同时,执法者则酣然入睡或被催眠。另一方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垄断造成了损害,相反,垄断带来了大量益处,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我们在第十五章探讨过这些争论。我们同意某些行业确实存在问题,例如,医疗行业和金融行业,但我们不认为美国普遍存在垄断问题。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即寡头垄断,是另一个大问题,有充分证据表明雇主想方设法地压低工人工资,使其低于竞争性工资。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对此进行辩论非常重要。随着科技进步和贸易发展,各个行业正在迅速变化,即使现行政策在今天奏效,也并不能保证其能一直如此。欧洲的监管者和政治家拥有不同想法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让我们看到不同政策的实际效果,即使他们的政策有时是出于针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主义。尽管垄断是非法的,但很难对其提起诉讼和进行监管,需要努力找到更好的办法。我们还认为,反垄断政策更积极地对企业并购加以审查,特别是防止大型企业收购潜在竞争对手,是一个好主意。或许举证责任应该更坚定地从监管机构转移到提议合并的公司。我们也赞同让亚马逊、脸书和谷歌在每次使用从用户那里获得的信息时都要付费。 [24] 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通过扩大,而非破坏市场,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强大。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丧失好工作的现象不仅伤害了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而且也伤害了其他人,因为这让许多社区遭到破坏,并摧毁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提高工资的公共政策,这是因为,如果任由劳动力市场自己决定工资,那么它不会考虑外部影响。提高工资可以通过工资补贴制度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实现。工资补贴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同时提高工资和利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长期以来一直倡议提高工资补贴,近年来保守派评论员奥伦·卡斯也提出同样的建议。 [25] 提高最低工资也会使工资增加。这样做是否会造成就业岗位流失则取决于最低工资增加的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不管怎样,企业利润都可能因此下降。因此,右派倾向于支持工资补贴,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左派则持相反观点。
我们并不反对工资补贴。在我们看来,关键是恢复就业岗位。但我们认为,近期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小幅提升最低工资不会导致就业机会丧失,只会将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线以下的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线之上,并使原本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线的工资同步增长,这很可能是为了维持某些重要的低薪岗位与其他岗位间的既有薪酬差异。1999年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后,英国低工资岗位的变化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两组证据都已在第十五章进行过论述。同时,许多美国人赞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在政治上可能比实施工资补贴更容易。
因此,我们赞同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当前的每小时7.25美元逐步提高到15美元。我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是将权力和金钱从企业向劳动力再分配这一更大目标的组成部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共有180万美国人的收入勉强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线,或者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其中约2/3的人从事服务业,主要是食品制备。 [26] 这些工作不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失掉的那些好工作,而是他们失去工作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工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与扩大社会安全网相似,将有助于缓解这种转型造成的冲击。
琼·罗宾逊曾描述所谓的专利悖论,即专利阻碍了扩散,反而使专利变得更多。 [27] 专利是一种公开授予的获取租金的许可,但其条件并不固定,而且面临强力游说。布林克·林赛和史蒂文·特莱斯 [28] 提出的观点认为,版权法和专利及许可要求,以及地方土地使用法规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利于寻租者和在位者,不利于挑战者,这一点正在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随着软件在许多行业中取代了有形资本,版权已得到更加积极地应用。建筑物可以用围栏和防护装置加以保护,但代码很容易被复制。版权、专利、土地使用法规和许可的存在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滥用这些权利进行向上再分配,即从竞争者和创新者向已经那些在位并试图通过保护自己地位来谋利的人进行分配,则需要对它们加以有力控制。有些观点认为,许多专利保护都是不必要的,并且有违公共利益, [29] 而目前做法的成本实际上远远大于收益。
在第十五章中,我们对游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谷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波音等大型企业的游说行为。但小企业在游说上的支出往往更多,虽然游说支出不是直接花费,而是通过他们所在的协会,例如美国商会、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和美国医学协会。这些组织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因为它们花了大笔资金,还因为它们的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在每个社区都有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州和每个国会选区都有代表。它们为了使这些小企业获得特殊待遇而进行游说,这些特殊待遇包括免除大企业需要遵守的法规,或者为房地产经纪人提供特殊的税收减免。 [30] 汽车经销商受到州法律的保护,这些法律禁止制造商直接向消费者出售汽车。医生及其协会严格控制医学院的招生人数,以减少医生的数量,从而维持他们的高工资。他们强制实施住院医师要求,有效地将外国医生排除在外;精英阶层的专业人士在防止来自外国竞争者的挑战方面做得更好,远远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
寻租行为和对小企业的保护是理解美国不平等现象的两个关键点。经济学家马修·史密斯、丹尼·雅根、欧文·齐达尔和埃里克·茨威格研究了企业及其所有者的税收数据,发现积极管理企业的企业家是导致顶层收入不均的关键因素。这些富有的企业主无论是在收入总额,还是在人数上,对于顶层收入不均现象的贡献都远超公司首席执行官。这些人主要从事“专业服务(如顾问、律师、特殊产品贸易员)或健康服务(如医生和牙医)。位居美国顶层0.1%的人口所拥有的典型企业是年销售额2000万美元,有百余名员工的区域性企业,例如,某家汽车经销商、饮料经销商或大型律师事务所” [31] 。这些企业几乎全部仰仗活跃于华盛顿或者州议会的游说团体,受到政府颁发的专门许可的保护,这些许可要求正是亚当·斯密口中“可说是用鲜血写就的法律” [32] 。律师为寻租者提供法律依据,指导他们推动制定或修改哪些法律法规,并帮助他们远离监狱。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行业协会或公司游说民选官员以获得保护。联邦和州立法者对这些法规的重视程度可能取决于选民对其所授出的许可保护的了解程度,以及在了解情况后选民对此的关心程度。我们怀疑选民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正在被一点点蚕食(或更糟)。因此,提供更多的信息,让选民知道是谁在进行游说,以及游说的内容和游说的后果,可能有助于降低这些游说活动的有效性。
在本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分化,后者面对包括死亡在内的一系列糟糕境遇。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学士学位,这个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好?
也许会吧。美国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科技发展提出新的需要时,又率先普及高中教育。在今天信息和通信革命的背景下,也许到了再次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使大学教育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
我们认为,很多现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本来可以获得学位,或者可以回炉深造并获得学位。他们会因此得到更好的待遇,同时其他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尽管可能益处没有那么明显。这尤其适用于那些有才华却未能上大学的人,无论他们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后者无疑更令人痛惜。许多人认为,这些人在今天重新接受高等教育比以前更加困难,因为高中毕业生重返大学校园的低成本机会越来越少。即使在今天,学士学位的经济回报也足以证明,上大学是很好的投资,不过风险确实存在,今天进入大学的人中,约有一半未能顺利毕业,他们可能会欠下债务却没能获得学士学位。目前进入大学的年轻人的比例持续上升,但获得学士学位的年轻人的比例基本未见增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是不幸的。显然,上过大学但未能毕业带来的好处相对有限,因此这种情况极其浪费。任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都会有所帮助,尽管让每个人都能免费上大学将耗费巨资,而且会将大部分利益分配给最不需要的人。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学士学位显然没有魔力,能使持有者免于被机器取代,或者在竞争中胜过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学士学位并不是一套能够保护个人免受变化影响的铠甲。正如50年前非洲裔美国人首当其冲地遭受失业和社区毁灭的打击,今天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身上一样,许多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很可能将在未来面临同样的冲击,这绝非耸人听闻,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并不能阻止这种结果出现。
不过,在其他富裕国家,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之间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分化。英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较低,尽管上大学的费用不断上涨,但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仍然迅速增加。德国有著名的学徒制,许多人选择接受学徒训练而不是上大学,这种制度培养了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对工作和技艺的极大自豪感。反对学徒制的一个论点是,学徒制将人与特定技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他们提供人文教育所应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然而,德国工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苦,在面对变化时接受再培训也是家常便饭。
我们认为,美国必须考虑其他选择。在美国,是否拥有学士学位所带来的不同境遇既是分裂性的,也对生产力毫无帮助可言。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主要是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却只有1/3的人成功地上了大学,这既是一种浪费,又极不公平。 [33] 那些没有成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有可能被打上失败者的烙印,要么从此自暴自弃,要么会认为社会制度不公,要么会两者兼而有之。 [34]
我们已经用很大的篇幅讨论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什么,以使我们可以消除绝望的死亡的流行病。其他国家是否受到同样的威胁?虽然我们不认为美国经历的一定会很快扩散到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确实可以从美国发生的事情中学到很多,其中很多是教训,即哪些事情不该做。
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教训是,其他国家应该维持目前对阿片类药物的管控。首先,欧洲(包括英国)的医生在开止痛药方面谨慎得多,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病人并没有因此而不得不忍受痛苦。欧洲国家的中年人显然没有出现疼痛症状流行的迹象。奥施康定等阿片类药物会在手术后立即在医院得到使用,但这样的处方在社区极为罕见。然而,阿片类药物生产商已经从烟草公司那里学到一课,并开始在全球推广使用其药物对抗疼痛。普渡制药旗下的国际子公司萌蒂制药向医生和其他倡导者支付费用,以换取他们推广阿片类药物,并鼓励医生克服“阿片恐惧症” [35] 。欧洲医学期刊上经常出现医生撰写的文章,主张放宽处方规定。美国的例子不应该被效仿,相反,它应该成为向其他国家发出的可怕警告,提醒它们为了企业利润而牺牲人们的生命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欧洲目前的政治形势几乎和美国政治一样令人担忧。许多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或者支持欧洲右翼政党或民粹主义政党的人,和众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一样,感觉在政治进程中被剥夺了权利。与美国一样,传统上代表劳工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看上去与代表资本方的政党已经没什么两样。同时,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虽不是所有),普通民众经历了十余年的工资增长停滞和紧缩,并导致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这其中也包括医疗保障。 [36] 正如我们对美国困境的描述,当劳工阶层越来越面对自动化和贸易的影响之际,政治家和企业非但没有努力帮助他们缓解这种影响的冲击,反而借机从中渔利,将收入从劳动力向上再分配给管理者和股东。在英国,紧缩政策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削弱了社会安全网。
英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并未出现持续下降,但其此前长期的持续增长已经放缓乃至停滞。英国10年的工资增长停滞尚无法与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工资下降相提并论,但这显然已经发出足够强的信号,警示政府不能自满。1945年之后,英国的工党政府建立了全球首个现代福利国家,如果它又成为率先摧毁福利制度的国家之一,导致其年青一代和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将资本主义视为敌人,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要想消灭绝望的死亡,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阻止或扭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工资下降的趋势。悲观主义者可能会说,我们正在经历贸易和技术突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只能坐等潮水退去,并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人在此期间被吞噬。
也许劳工阶层的困境与工资、工作或任何其他外部环境都没有关系,而是如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所说,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丧失了勤奋和其他美国人固有的美德。 [37] 如果是这样,那么政策是否能起到帮助作用不得而知,真正需要的是道德或宗教复兴。对这个观点我们无法苟同。在本书专门讨论劳动力市场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无论在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在工资增长率方面都在下降,这种现象在男性中已经存在多年,近年来又扩散到女性中。参与率和工资同步下降清楚地表明,雇主需要的低技术水平工人数量变少了。由于工作岗位减少,工人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降低),要么接受更差的工作(工资降低)。如果导致参与率降低的是工人勤奋程度下降(工作意愿降低),那么随着雇主争夺更少的可用工人,工资应该上涨,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死亡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任何其他富裕国家,都未曾出现绝望的死亡。我们认为,美国的绝望和死亡程度反映了美国的具体政策和环境。美国医疗制度对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无异于一场灾难,更严重的是,它正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以便使少数富人更加富有。医药公司通过使病人成瘾和使普通百姓无法享受数十年医疗进步的定价策略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贸易和自动化使劳工阶层处于更脆弱的境地,另一方面,公司和立法者并没有抓住机会加强社会安全网,以尽量减轻伤害。如果说两者做了什么,那就是利用劳动力的弱势地位压低工资和向上分配收入,换言之,从劳动力手中夺取财富并分配给资本,从普通人手中夺取财富并分配给精英。与此同时,政治体系受制于游说集团和立法者对财大气粗支持者的需要,已经日益成为各种商业和专业人士角逐利益的战场。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国会本应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们。法律本应保护弱者不受强者寻租行为的侵害,但其越来越站到勒索者一方。诺丁汉郡治安官搬到了华府定居,良心警察已经离开,而罗宾汉并没有出现。
不过,我们依旧感到乐观。我们曾考虑以“资本主义的失败”作为本书的书名,但最终选择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拥有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让人民为它服务。资本主义需要更好的监督和管理,并由国家全盘接管商业。民主可以面对挑战,国家可以做得更多,并做得更好,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政府的危险,更大的政府意味着更多的寻租空间和更大的不平等 [38]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支持市场而非反市场的,理应得到左右双方的支持,无论是右翼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左翼过度不平等的批评者。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比现行税收制度更公平的制度,但我们不赞同优先考虑对富人课以重税,因为我们不认为不平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换言之,当前的制度令处于财富顶端的少数人获得巨额不义之财,而众多普通人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机会。我们的观点是,限制寻租和减少掠夺将使富人受到控制,减少财富顶层的不公平收入,同时不必对被普遍视为公平收入的那一部分收入或财富征收高额税赋。
美国的民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它远未消亡,如果人们如同在一个世纪前的进步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那样,努力推动它,民主将可以再次发挥作用。
对于坚持读到最后的读者来说,我们的建议应该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建议大多是针对我们对已经发现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便如此,把它们汇总在一起仍然有一定意义。我们无法详细描述政策建议,并且既无意,也无能力在众多人已经全面阐述的医疗改革和社会安全网设计方案中做出选择。然而,我们希望,严重的死亡流行病,以及寻租和向上再分配所造成的极端不平等局面将创造一个机会,使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中的改革计划得以实施。这是我们早就该采取的行动。
[1] Amartya K. Sen,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martya K.Sen, 2006, “What do we want from a theory of just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103(5),215–38.
[2] Anthony B. Atkinson, 1970, “The measure ment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 ory , 2, 224–63.
[3] Derek Parfit, 1997, “Equality and priority,” Ratio , 10(3), 202–21.
[4] Peter Diamond and Emanuel Saez, 2011, “The case for a progressive tax: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5(4),165–90.
[5] Abby Goodnough, 2018, “This city’s overdose deaths have plunged. Can others learn from it?,”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25, https:// www.nytimes.com/2018/11/25/health/opioid -overdose-deaths-dayton.html.
[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9, “Prescription opioid data,” last reviewed June27, https:// www.cdc.gov/drugoverdose/data/prescribing.html.
[7] Kenneth J. Arrow,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73.
[8] Nicholas Timmins, 2009, “The NICE way of influencing health spend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ir Michael Rawlins,” Health Affairs , 28(5), 1360–65, https://doi.org/10.1377/hlthaff.28.5.1360.
[9] Arrow, “Uncertainty,” 967.
[10] Edward R. Berchick, Emily Hood, and Jessica C. Barnett, 2018,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7 , report no. P60-264, US Census Bureau,September, https://www .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8/demo/p60-264.html.
[11] Victor R. Fuchs, 2018, “Is single payer the answer for the US health care syste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19(1), 15–16,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7.18739.
[12] Victor R. Fuchs, 2018, “How to make US health care more equitable and less costly: Begin by replacing employment- based insur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320(20), 2071–72, 2072,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8.16475,2072.
[13] Ezekiel J. Emanuel and Victor R. Fuchs, 2007, A comprehensive cure: Universal health care vouchers , Discussion Paper 2007-11,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http://www.hamiltonproject.org/assets/legacy/files/downloads_and_links/A_Comprehensive_Cure-_Universal_Health _Care_Vouchers.pdf.
[14] Dylan Scott, 2019, “How to build a Medicare- for- all plan, explained by somebody who’s thought about it for 20years,” Vox, January28, https:// 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9/1/28/18192674/medicare-for-all-cost-jacob-hacker. See also JacobS. Hacker, 2018, “The road to Medicare for everyone,” American Prospect ,January 3.
[15] BBC News, 1998, “Making Britain better,” July1, http:// news.bbc.co.uk/2/hi/events/nhs _at_50/special_report/119803.stm.
[16] Anthony B. Atkinson,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Data and explanations,”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 49(4), 479–513.
[17] Kwame Anthony Appiah, 2018, The lies that bind: Rethinking identity , Liveright.
[18] 普遍基本收入又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政策概念,指在不审查任何条件与资格的情况下,由政府或组织定期定额发放给全体成员(人民)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译者注
[19] Philippe van Parijs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2017,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 Emma Rothschild, 2000, “A basic income for all: Security and laissez- faire,”Boston Review , October1, http:// bostonreview.net/forum/basic-income-all/emmarothschild-security-and -laissez-faire.
[21] Herbert Simon, 2000, “A basic income for all: UBI and the flat tax,” Boston Review , October1, http:// bostonreview.net/forum/basic-income-all/herbert-simon-ubiand-flat-tax.
[22] Hilary W. Hoynes and Jesse Rothstein, 2019,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the US and advanced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25538, February, https:// www .nber .org /papers /w25538.
[23] Robert H. Frank, 2014, “Let’s try a basic income and public work,” Cato Unbound , August11, https:// www.cato-unbound.org/2014/08/11/robert-h-frank/lets-trybasic-income -public-work.
[24] Eric A. Posner and E. Glen Weyl, 2018,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 racy for a just societ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 Edmund Phelps, 2009, Rewarding work: How to restore participation and self support to free enterpri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en Cass, 2018,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 ca , Encounter Books.
[26]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8, “Characteristics of minimum wage workers,2017,” BLS Reports, Report 1072, March, https://www.bls.gov/opub/reports/minimumwage/2017 /home.htm.
[27] Joan Robinson, 1956,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 Macmillan, 87.
[28] Brink Lindsey and Steven M. Teles, 2017, The captured economy: How the powerful enrich themselves, slow down growth, and increase inequa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Lindsey and Teles. See also Dean Baker, 2016, Rigged: How globaliza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economy were structured to make the rich richer ,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30] Robert D. Atkinson and Michael Lind, 2018, Big is beautiful: Debunking the myth of small business , MIT Press.
[31]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2019, “Capi t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4), 1675–1745, 1677.
[32]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 bk. 4.
[33] Cass, Once and future worker .
[34] Michael J. Sandel, 2018, “Popu 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open Dem-ocracy, May9, https:// www.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 -democracy/.
[35] Harriet Ryan, Lisa Girion, and Scott Glover, 2016, “Oxy Contin goes global — ‘We’re only just getting started,’” Los Angeles Times , December18, https:// www.latimes.com/projects /la-me-oxycontin-part3/.
[36] Ellen Barry, 2019, “‘Austerity, that’s what I know’: The making of a young UK socialist,”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24, https:// www.nytimes.com/2019/02/24/world/europe/britain -austerity-socialism.html.
[37] Charles Murray, 2012,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 ca, 1960–2010 ,Crown.
[38] Angus Deaton, 2017, “Without governments would countries have more inequality, or less?,” Economist , July 13.
许多人对本书贡献良多,对于他们的建议、意见和评论我们深表感谢。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奥利·阿申费尔特、丽莎·伯克曼、蒂姆·贝斯利、埃里克·凯恩、戴夫·卡德、苏珊·凯斯、丹尼尔·钱德勒、安德鲁·切尔林、吉姆·克利夫顿、弗朗西斯·柯林斯、珍妮特·柯里、戴维·卡特勒、杰森·道可特、比尔·伊斯特利、贾妮丝·埃伯利、汉克·法伯、维克·富克斯、杰森·富曼、莱纳德·盖洛萨、黛比·吉特曼、达娜·戈德曼、奥利弗·哈特、苏珊·希金斯、乔·杰克森、丹尼·卡尼曼、阿里伊·卡普滕、莱恩·肯沃西、珍娜·科瓦尔斯基、南希·克里格、伊莉安娜·库兹伊姆科、安娜·莱姆比、戴维·利普顿、阿德里安娜·雷勒斯-穆妮、特雷冯·洛根、迈克尔·马尔莫特、萨拉·麦克拉南、埃伦·米拉、爱丽丝·穆尔霍夫、弗兰克·纽波特、朱迪思·诺瓦克、巴拉克·奥巴马、萨姆·普雷斯顿、鲍勃·普特南、朱莉·雷、伦纳德·谢弗、安德鲁·舒勒、乔恩·斯金纳、吉姆·史密斯、乔·斯蒂格利茨、亚瑟·斯通、鲍勃·蒂戈尔、约翰·范·雷宁、诺拉·沃尔科夫、戴维·威尔、吉尔·韦尔奇、密克隆·韦耶内斯、丹·威克勒、诺顿·怀斯、马丁·沃尔夫、欧文·齐达尔和路易吉·津加莱斯。
我们尤其需要感谢并非经济学家的诸位友人,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开阔思路,并使我们避免了犯下一些错误。如果本书中仍然存在任何错误和误解,希望他们能够原谅,对此我们将承担全部责任。本书探讨的议题无法以单一学科涵盖,对于两位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一次令我们深感谦卑的经历,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专业存在如此多的疏忽和谬误。我们从众多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医生和流行病学家那里得到了大量宝贵的帮助。
2019年4月,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坦纳人类价值观”讲座中介绍了本书的一些材料。在此我们希望感谢坦纳基金会的支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盛情款待,并感谢在此期间举办的许多正式讨论和有益的交谈。
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普林斯顿大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学术环境,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也为学术研究在政策问题上发挥作用提供了大力支持。我们还长期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合作,其前任主席吉姆·波特巴和已故的马蒂·费尔德斯坦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迪顿是南加州大学的首席教授,在此他希望感谢他在南加州大学自我报告科学中心、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和伦纳德·D.谢弗卫生政策和经济中心的诸位同事。同时,作为盖洛普的资深科学家,他还希望感谢盖洛普的各位同事,他们一直以来都像取之不尽的源泉,提供了大量资料支持、数据,以及无上的热情和绝佳的创意。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是一家理想的出版社。我们希望感谢杰姬·德莱尼、乔·杰克逊、特丽·奥波雷、卡罗琳·普里迪、詹姆斯·施奈德以及其他许多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我们还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慷慨支持,本书中的内容综合了几项得到不同拨款支持的研究项目。已故的理查德·苏兹曼曾在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这一最高级别的社会调查机构任职,他对我们在人口健康状况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主要支持。对于我们以个人身份或者双方联合从下列机构获得的研究基金,包括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以及全国经济研究所(R01AG040629、P01AG05842、R01AG060104、R01AG053396、P30AG012810-25)、普林斯顿大学(P30AG024928)和南加州大学(R01AG051903),我们同样深表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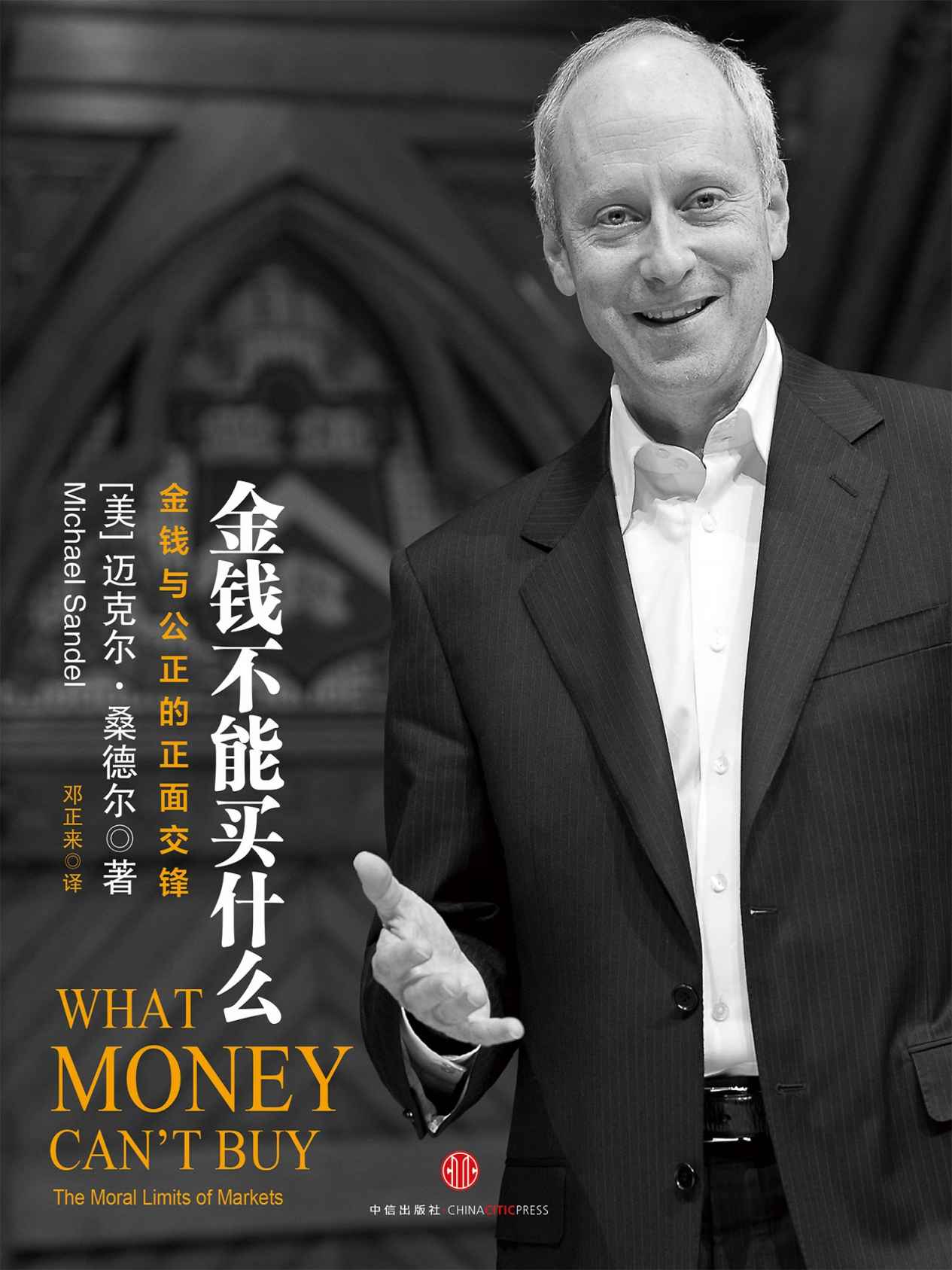
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几个例子: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 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1]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 pool lane):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2]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 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3。 [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4]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5]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 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1 500~25 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6]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7]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8]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9]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 500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10]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 000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11]
·在国会山为1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12]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13]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14]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15]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16]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17]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那种侵蚀倾向。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国雇佣军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却侵蚀了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 [18]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或者,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
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money’s writ)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是我至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可以推动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并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哲学框架。
即便你赞同我们需要抓住这些有关“市场之道德”的大问题,你仍可能会怀疑我们的公共话语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这个担忧合情合理。任何重新思考市场角色和范围的尝试,都应当首先承认下面两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碍。
一个是市场观念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来市场失败最惨痛的后果面前亦复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公共话语中的怨怼和空泛。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不相关的。
第一个障碍很令人困惑。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此前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的做法(这种做法跨越政治范围盛行了30年)所作的一个道德裁定。曾经无所不能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几近崩盘以及对大量紧急援助的需求(以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看似毫无疑问地引发了人们对市场的重新思考。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曾长期扮演市场必胜论信念的高级传教士;即便像他这样的人后来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态度”承认说,他对市场自我纠错力量的信心被证明是错误的。 [19]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是一份积极推广市场信念的英国杂志,它当时一期的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经济学教科书,标题则是“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最终走向了毁灭。其后想必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代,亦即一个重新追问市场信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证明,社会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
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所破坏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2011年,多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上,美国公众所谴责的更多的是联邦政府而非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其比率要高于2∶1。 [21]
这场金融危机将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抛进了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之中,并且让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然而即便这样,它也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问题进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国所导致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却是茶党运动的兴起,然而茶党运动对政府的敌意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甚至都会使当年的罗纳德·里根深感汗颜。2011年秋天,“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抗议者们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大城市频频集会。这些抗议者们把他们的矛头直指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权力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在对政府采取紧急援助措施方面表达一种民粹式的愤慨。 [22]
除了这类抗议声音外,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严肃辩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仍严重缺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其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仍在对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是现在的争论更多了一点党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说服力而已。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能力代理公共善,或者说,没有能力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公民对这种政治体制越来越感到灰心,同时对政治的理想也日渐幻灭。
公共话语的这般窘况乃是开展关于市场道德局限之辩论的第二大障碍。在一个政治争辩主要由有线电视上的吵架比赛、广播讨论节目里党派性极强的谩骂和国会中意识形态性的扔食品大战所组成的时代里,很难想象人们会把一种关于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理性公共辩论视作评价生育、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资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确途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辩论是可能的,而且还会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发生机。
一些人认为我们所怨怼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道德信念:太多的人太过深切、太过固执地信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且还想把这些信念强加给所有其他人。我认为,这种看法误读了我们的窘境。我们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争辩,而恰恰是争辩得太少。我们的政治之所以过于激烈,实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而且也未能关注人们所关切的那些重大问题。
当代政治的道德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将“良善生活”的观念从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排挤出去。为了避免派系纷争,我们往往坚持认为,当公民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他们应当将他们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抛在脑后。尽管这种观点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不想把良善生活的争论纳入政治的做法却为市场必胜论和坚持信奉市场逻辑的做法扫清了道路。
当然,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当。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笔钱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购买一个肾脏,而另一个同意此桩买卖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经济学家问的唯一问题就是“多少钱”。市场不会指责这种做法,而且它们也不会对高尚的偏好与卑鄙的偏好加以区别。交易各方都会自己确定所交易的东西具有多大价值。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争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
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有能力确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以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展开这种辩论还会经由允许各种彼此冲突的良善生活观念进入公共场所而使我们的政治具有生机。再者,这些辩论又将如何展开呢?如果你认为买卖某些物品会腐蚀或贬低它们,那么你肯定会相信一些评价这些物品的方式要比其他方式更加适宜。腐蚀某种行为(例如父母身份或公民资格)的说法很难讲得通,除非你认为某些为人父母或者做一个公民的方式要比其他的方式更好。
与此类似的道德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市场进行若干限制的理由。我们不允许父母贩卖他们的子女,或者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坦率地讲,就是道德判断。因为我们相信,售卖这些东西乃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他们/它们,而且还会形成不好的态度。
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它要求我们在公共领域中一起来思考如何评价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善品。认为一种更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讨论(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会使人们对每个有争议的问题都达成共识,那是愚蠢的。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时,它也会使我们更加明白,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当我们考虑市场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华尔街的各大银行及其不计后果的行径,也会想到对冲基金、紧急援助和政府调控改革。但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道德挑战和政治挑战,却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平常的性质——也就是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范围。
没人喜欢排队等候。有时候你可以花钱插队。人们很早就知道,在高档饭店里只要给领班塞一笔可观的小费,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时不用排队等候。这种小费有点儿像贿赂,因而只能悄悄地给。没有一家饭店会在窗户上贴出布告说,愿意给领班50美元的人可以立刻得到位子。然而,近年来,出售插队权利的现象已渐渐公开化,并且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
等候机场安检的长龙,使乘机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蛇形长队后等候。购买了头等舱或者商务舱机票的人可以走优先通道,先行通过安检。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把这称为“快速通道”(Fast Track),而且这项服务还可以使多花钱的乘客在护照和移民检查点插队。 [1]
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头等舱的机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开始为经济舱旅客提供购买插队特权的机会。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就会为你提供从丹佛到波士顿的优先登机权,此外还可以享受在安检点插队的特权。在英国伦敦,卢顿机场为乘客提供了一种更加实惠的快速通道选择方案:要么在长长的安检队列后面排队等候,要么掏3英镑(约合5美元)排到队伍的前面去。 [2]
评论家抱怨说,机场安检的快速通道不应当拿来出售。他们辩称道,安检是一项国防举措,而不是像飞机上的紧急门座位或者优先登机权那样的便利措施;所有乘客都应当平等承担让恐怖分子远离飞机的责任。航空公司则回应道,所有乘客都将接受同样严格的安检,只是等待的时间因乘客支付的费用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主张,只要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样的安检,那么在安检队列中插队便是它们应当可以自由出售的一项便利措施。 [3]
游乐场也开始着手出售插队的权利。一直以来,为了享受最受欢迎的游乐项目和景点,游客总得花好几个小时排队等候。现在,好莱坞环球影视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和其他游乐场为游客提供了一种不用等候的做法:如果你愿意支付大约两倍于一般票价的价钱,你就可以购得一张排到队伍最前面去的通行证。与在机场安检点享有插队特权相比,优先享受“木乃伊的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Mummy)这一游戏有可能在道德上更令人可以接受。但是,一些观察家仍对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它腐蚀了健全的公民习惯。一位评论家写道:“过去,所有去主题公园度假的家庭都会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队等候,而现在,对大家一视同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有趣的是,游乐场常常会掩饰它们所出售的特权。为了避免激怒普通游客,一些游乐场会领着他们的贵宾级客户从后门或者边门进去;另一些游乐场则会派专人护送他们去插队。这种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进行,表明了即使在游乐场里,花钱插队也是有悖于这样一种理念的,即公平意味着排队等候。但是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的售票网站却没有这么躲躲闪闪,它公开兜售价值149美元的队伍前面通行证:“凭此证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去,优先享受或观赏所有的游乐项目、表演和景点。” [5]
如果你讨厌游乐场的插队现象,那么你可以选择像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这样的传统景点。你只要掏22美元(儿童票16美元),就可以乘坐电梯到达86层的观景台,尽览纽约市的壮丽景观。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景点每年都会吸引好几百万名游客,而且有时候等候电梯也要花上几个小时。于是,帝国大厦现在也推出了自己的快速通道服务项目。每个人只要掏4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快速通行证,可以在安检处和乘电梯时插队。掏180美元为一个四口之家购买快速登上观景台的特权似乎价格不菲,但是正如该售票网站所指出的:“快速通行证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可以不用排队便直达最美的景点,并且可以使你充分地利用你在纽约和帝国大厦的时间。” [6]
在美国各地的免费公路上,也可以看到快速通道不断增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自驾出行者可以通过付费来躲开汽车长龙,从而使用高速运行的快速通道。此举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人共用车专用道”。在美国,很多州都希望减少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现象,于是它们为愿意合伙用车的人开设了快速通道。如果独自驾车者被发现使用了“多人共用车专用道”,就会遭到巨额罚款。于是,一些司机在乘客座上放上充气娃娃,希望用此举骗过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在电视喜剧片《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的一集中,拉里·戴维(Larry David)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最终买到了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行驶的权利。有一天,他在去看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时遇到了交通堵塞。于是他雇用了一个妓女,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雇她拼车去体育场。果不其然,经过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的疾驶,他顺利地在比赛开始前赶到了体育场。 [7]
现在,很多驾车族不需要雇人拼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交通高峰时段,独自驾车者只要支付最多10美元就可以买到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的权利。圣迭戈、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丹佛、迈阿密、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城市现在都在出售快速通行的权利。此项费用一般因交通状况而异:交通状况越拥堵,费用就越高。(在大多数地方,载有两名以上乘客的车辆仍然可以免费使用快速通道。)在洛杉矶东部的河畔高速公路的高峰时段,车辆在免费公路上只能以每小时15~20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付费客户在快速通道上则可以以每小时60~65英里的速度疾驶。 [8]
一些人反对出售插队权利的主意。他们认为,快速通道项目的激增强化了富人的优势,而使穷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反对者把这种付费快速通道称作“雷克萨斯专用道”,并认为此举对于一般收入的驾车族来说是不公平的。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为快捷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没什么错。联邦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为次日送达服务收取额外费用。各地的干洗店也为当日可取的服务收取额外费用。但是没有人抱怨,联邦快递加急投递你的包裹或者干洗店加急洗熨你的衬衣是不公平的。
对经济学家而言,排队购买商品和获得服务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是低效的;这表明价格体系没有匹配好供需关系。让人们在机场、游乐场和高速公路上通过付费来获得快捷服务,就是通过让人们为自己的时间定价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率。
即使在不允许购买插队权利的地方,有时候你也可以雇人替你排队。每年夏天,纽约市公共剧院(New York City’s Public Theater)都会在中央公园免费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晚场演出的戏票在下午1点钟开始派发,但是人们却会在好几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排队。2010年,当著名演员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出演《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夏洛克时,门票尤其紧俏。
很多纽约人都很想看这场演出,但却没有时间排队。诚如《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所报道的,这种困境催生了一个小型产业——有人为那些愿意花钱买方便的人提供代为排队取票的服务。这些人在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list)和其他网站上宣传他们的这种服务。作为排队和漫长等候的酬劳,他们可以向无暇排队的客户索要(每张免费戏票)高达125美元的报酬。 [9]
纽约市公共剧院曾尝试阻止收费排队者的生意,声称“这种生意有悖于本院免费在中央公园上演莎翁戏剧的精神”。该公共剧院是一家公共资助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欣赏到伟大的剧目。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向克雷格列表网站施加压力,要求它停止刊登代人领票和替人排队的服务广告。他指出,“兜售本应免费的戏票,剥夺了纽约人享受纳税人供养的机构所提供的福利”。 [10]
中央公园并不是唯一替人排队等候就可以挣到钱的地方。在华盛顿特区,替人排队的生意也迅速成为政府机构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召开立法预案听证会时,他们会给媒体预留一些席位,余下的席位则按照“先到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原则向普通公众开放。人们为了旁听这样的听证会可能需要提前一天或几天就开始排队,有时候还要在雨中或者严寒的冬季排队,当然这取决于听证会的议题和会场席位的数量。企业游说者们非常热衷于参加这些听证会,其目的是为了在听证会茶歇的时候与立法者攀谈,并了解对其行业具有影响的立法的情况。但是游说者们却不愿意为了得到一个位子而花好几个小时去排队。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支付数千美元给专业的排队公司,使其雇人替他们排队。
排队公司招募退休人员和信差,并且越来越多地雇用无家可归者,让他们在严寒酷暑中为他人排队占座。替人排队者起先是排在大楼外面,尔后随着队伍的前移,他们慢慢地进入国会办公大楼的大厅,排在听证室的外面。听证会快开始时,衣着考究的游说者们纷纷赶到,并同衣衫褴褛的替人排队者交换位置,然后再确认他们在听证室里的席位。 [11]
排队公司向游说者们收取每小时36~60美元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得到国会委员会听证会的一个旁听座位,至少可以赚1 000美元。替人排队者个人拿到的酬劳是每小时10~20美元。《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社论反对这一做法,称此举不仅“有辱”国会的尊严,而且也是“对公众的藐视”。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士——曾试图禁止这种做法,但却无功而返。她说:“那种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像买票听音乐会或者看橄榄球赛一样,买到国会听证会的旁听席位的想法,让我感到愤慨。” [12]
这种生意最近还从美国国会扩展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就重大宪法案件举行口头辩论听证会时,人们很难进入现场旁听。但是如果你愿意花钱,那么你可以雇一个人替你排队,从而得到美国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前排座位。 [13]
一家叫“替人排队网”(LineStanding.com)的公司把自己称作“国会排队业界中的领头羊”。当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提议通过立法来禁止这种做法的时候,这家网站公司的老板马克·格罗斯(Mark Gross)则为这种做法进行了辩护。他将排队比作亨利·福特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生产流水线上的每名工人都要对自己特定的工作负责。”游说者擅长出席听证会并“分析所有的证词”,参议员和众议员擅长“做出明智的决策”,而替人排队者则擅长排队等候。格罗斯说,“劳动分工使美国成为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替人排队看上去像是一种怪异的做法,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它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本分且正当的工作”。 [14]
职业替人排队者奥利弗·戈梅斯(Oliver Gomes)赞同上述观点。做这份工作之前,他正住在一家流浪汉庇护所里。当他为一名参加气候变化问题听证会的游说者排队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采访了他。戈梅斯告诉记者说:“坐在国会大厅里让我感觉好一些。这提升了我,你知道,这让我感觉自己也许就属于这里,也许我可以在这个微小的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15]
但是,给戈梅斯这样的人机会,意味着一些环保主义者可能会失去机会。当一些环保主义者打算参加气候变化问题的听证会时,他们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因为游说者雇来的替人排队者早已占满了听证会所有开放的席位。 [16] 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如果环保主义者真的想要参加这场听证会,那么他们自己也可以熬夜来排队。或者,他们也可以雇用无家可归者来为他们排队。
有偿替人排队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最近,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听说替人排队业务在北京的顶级医院里也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中国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公立医院和卫生所的经费削减,尤其是农村地区。因此,如今农村的病人千里迢迢前往首都的各大公立医院,在挂号厅里排起了长队。他们熬夜排队,有时候还要排上好几天,就是为了能够挂上号看上病。 [17]
一个门诊号很便宜,只要14元(约合2美元),但是却很难购到。一些急于挂上号的病人,不是日夜排队,而是从黄牛那里买挂号单。黄牛们从供需关系的巨大缺口中挖掘出了商机。他们雇人排队挂号,然后再把挂号单以数百美元的价格转手——这个价格要高于一个普通农民几个月的收入。特需专家门诊号的价格尤其昂贵——黄牛们似乎把这种挂号单当成了世界棒球职业联赛的包厢票来兜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描绘了北京一家医院挂号大厅外黄牛们兜售门诊号的场景:“唐大夫!唐大夫!谁想要唐大夫的挂号单?风湿免疫科的!” [18]
倒卖门诊号的做法有些可恶。这种做法首先奖励了可恶的黄牛党,而不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唐大夫完全有理由质问,如果一个风湿科门诊号值100美元,那么大部分钱为什么应该归黄牛党所有,而不是为唐大夫或者唐大夫的医院所有。经济学家可能会赞同并建议医院提高挂号收费。事实上,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设了特需窗口,在那里,挂号费更贵、排队等候的人也更少。 [19] 医院的这种高价门诊号窗口,就像是游乐场无须排队等候的优先通行证或机场的快速通道一样——即为付费插队提供的一个机会。
但是,不管谁从这种供不应求中获利,是黄牛党抑或是医院,通往风湿免疫科的快速通道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难道仅因为一些患者支付得起额外加价,他们就可以插队看病吗?
北京医院的特需挂号窗口和黄牛党以非常生动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对美国越来越普遍的更为精妙的插队行为——“特约医生”的兴起——提出上述问题。
虽说美国的医院里没有挤满黄牛党,但是去看病常常还是要等很久。你需要提前几周、有时候几个月就预约医生。当你如约就诊时,还需要在候诊室等很久,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匆匆地和医生会面10或15分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险公司不会为日常的门诊治疗付给初级诊疗医生很多钱。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每个内科医生通常至少要有3 000个病人,每天经常要匆匆接诊25~30个预约病人。 [20]
许多病人和医生都对这种制度安排感到沮丧,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医生几乎没有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病情或回答病人的问题。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开始为病人提供一种更为贴心的服务,即“特约医疗”(concierge medicine)。就像五星级酒店礼宾部的侍应生一样,特约医生为病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对于缴纳年费(1 500~25 000美元不等)的病人而言,可以确保当日就诊或次日就诊、无须等候、充分问诊、全天24小时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手机联络到医生。如果你需要看一位顶级专家,那么你的特约医生会帮你搞定一切。 [21]
为了提供这种贴心服务,特约医生大幅削减了他们原来接诊的病人的人数。那些决定将其一般业务转为特约医疗服务的医生会给他们的现有病人发一封信函,让他们做出选择:要么缴纳年费来享受新的无须等待的服务,要么另找其他医生。 [22]
成立最早的、收费最贵的特约医疗服务机构之一,是1996年成立于西雅图的“MD2”公司(MD Squared)。对于缴纳年费(个人年费为15 000美元、家庭年费为25 000美元)的个人而言,该公司承诺可以使他“绝对、无限和排他性地享有私人医生的服务”。 [23] 每位医生只为50个家庭服务。正如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所解释的:“我们所提供的是周到、高档的服务,因此我们只能为少数精挑细选的客户提供服务。” [24] 《城乡》(Town & Countr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MD2”的候诊室“更像是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 而不像是医生的门诊室”。但是,即使如此,几乎也没有几个病人去那里看病。大部分去那里看病的病人是“首席执行官和老板,他们不想花时间去诊所看病,而喜欢在家里或办公室这样的私密环境中接受治疗”。 [25]
其他一些特约服务机构则为中上层人士服务。“MDVIP”是一家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营利性特约服务连锁公司。它收取1 500~1 800美元的年费,提供当日就诊和即时服务(全天候热线服务),并且接受由医保支付常规医疗项目的做法。由于加盟这个连锁公司的医生把其病人的人数削减到了600人,所以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每一位病人看病。 [26] 这家公司向病人承诺:“他们在就诊看病时无须再等待。”《纽约时报》报道说,“MDVIP”在博卡拉顿的候诊室里摆放了水果沙拉和海绵蛋糕。但是,由于几乎没有病人等候看病,所以候诊室里的食品也常常无人问津。 [27]
对于特约医生和付费客户来说,医疗就应该像特约医疗这样。医生每天只看8~12个病人,而不是30个病人,而且他们的收入仍可以远超同行。加盟“MDVIP”的医生可以得到客户所缴年费的2/3(公司得到1/3)。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特约医疗服务机构有600个病人,那么光算年费,一年它就有60万美元入账,这还不算保险公司给予的偿付。对于支付得起这种服务年费的病人来说,时间充裕的会诊和全天候的医疗服务乃是一种值得花钱享受的奢华。 [28]
当然,特约医疗服务的缺点是它只为少数病人提供服务,而将大多数病人都推到了其他医生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患者队列中。 [29] 因此,它招致了与那种反对所有快速通道项目的观点一样的反对意见:特约医疗服务对于那些仍滞留在拥挤行列中受罪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特约医疗服务肯定不同于北京的特需门诊服务和倒卖门诊号的做法。那些无钱享受特约医生服务的人,一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体面的医疗服务,而在北京买不起黄牛门诊号的患者则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排队等候挂号。
但是这两种做法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二者都使得富人可以在享受医疗服务时插队。插队行为在北京比在博卡拉顿更加显得明目张胆。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厅里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而博卡拉顿候诊室中摆放的海绵蛋糕却无人问津;前者的异常喧嚣与后者的安静似乎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当享受特约服务的病人按约赴诊时,他们已经通过付费的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插队。
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这几种情形都刻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在机场和游乐场、在国会走廊和医生的候诊室,“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正在被“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所取代。
而这种转变反映了某种更大的问题,即金钱和市场越来越侵入此前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控的各个生活领域。
出售插队权并不是这种趋势中最严重的例子。但是,认真思考替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和其他插队形式的对错,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市场逻辑的道德力量和道德局限。
雇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有什么错吗?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错。他们对排队伦理没有太多同情。他们问道,如果我想雇用一个无家可归者替我排队,为什么其他人应当抱怨呢?如果我愿意转售我的票或门诊号,而不是使用它,为什么其他人应当阻止我这么做呢?
赞同市场伦理压倒排队伦理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尊重个人自由的观点,另一个是关于福利或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观点。第一种是自由至上论的观点。它主张,人应当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买卖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任何权利。自由至上论者反对禁止倒票或倒卖门诊号的法律,其理由与他们反对禁止卖淫或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法律通过干涉成年人的选择而侵犯了个人自由。
支持市场伦理的第二种观点是经济学家更为熟悉的功利主义。它认为,市场交换会惠及买卖双方,因而可以改善我们的集体福利或社会功利。我和替我排队的人达成交易这个事实,证明我们在结果上都是受益者。只需要支付125美元而无须排队等候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戏剧肯定会使我受益,否则我不会雇人替我去排队。排几个小时队挣得125美元也肯定会使替人排队者受益,否则他就不会接这份活。我们俩因为我们的交换而在结果上都获得了好处,因而我们的功利也都增加了。这就是经济学家说自由市场有效分配物品的意义所在。通过允许人们进行互惠的交易,市场把物品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人,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的同事格雷戈·曼昆(Greg Mankiw)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的作者。他用倒票的例子阐明了自由市场的优点。他首先解释说,经济效率意味着以“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都得到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物品。然后他又指出,自由市场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将物品分配给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购买者,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 [30] 让我们考虑一下黄牛党的情形:“如果经济要有效地配置其稀缺资源,那么物品就必须分配给那些最珍视其价值的消费者。倒票就是市场如何达到有效结果的一个例证……通过索要市场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黄牛党有助于确保那些有最大意愿付费购票的消费者真正拿到票。” [31]
如果自由市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票贩子和替人排队公司就不应当因为违反排队伦理而受到指责;相反,他们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把被低估的物品送到了那些最愿意出价购买它们的人手里,从而提高了社会功利。
那么,赞同排队伦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人们为什么要设法从纽约中央公园或者国会山清除那些收费排队者和票贩子呢?在中央公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纽约市公共剧院的发言人给出了如下理由:“这些人抢走了那些渴望去中央公园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的位子和门票。我们想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 [32]
这个观点的第一部分存在缺陷。受雇替人排队者并没有减少观看演出的人数,而只是改变了观看演出的人。诚然,正如该发言人所宣称的,如果替人排队者不拿走这些门票,那么排在队列末尾很想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就可以拿到这些票。但是,那些最终拿到这些票的人也很想观看这场演出,所以他们才花125美元雇人替他们排队。
这个发言人很可能是想说,对于那些掏不起125美元的人来说,倒票行为是不公平的。倒票把普通民众置于不利的境地,使他们更难得到门票。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论点。当替人排队者或黄牛拿到一张票的时候,某个排在他后面的人就可能因为出不起票贩子的要价而拿不到票。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可能会这样回答:如果剧院真心想让渴望观看这场演出的人进场看戏并使演出带来的快乐和愉悦最大化,那么剧院就应当让那些最珍视演出价值的人得到门票。这些人就是乐意出最高价钱来购票的人。因此,让那些能够从观看这场演出中获得最大快乐的观众进场观看演出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由市场去运作——要么以市场能够承受的任何价格售票,要么允许替人排队者和黄牛把票卖给出价最高的竞购者。让那些愿意出最高价钱购票的人得到门票,乃是确定谁最珍视莎翁戏剧的最好办法。
但是这个论点无法让人信服。即使你的目的是使社会功利最大化,自由市场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比排队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购买一种物品的意愿并不能证明谁最珍视这种物品。这是因为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也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那些最想观看莎翁戏剧或波士顿红袜队(the Red Sox)比赛的人,也许买不起门票。而且在某些情形中,那些花最高价钱买票的人根本不珍视这样的观看体验。
比如,我注意到那些坐在棒球场昂贵席位上的人经常迟到、早退。这让我疑惑他们到底有多重视棒球比赛。他们购得本垒板后面的座位的能力,有可能更多的是与他们的钱袋大小有关,而与他们对棒球比赛的热情无关。他们肯定没有一些球迷那么重视棒球比赛,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球迷——尽管他们买不起昂贵的包厢票,但是却能够说出首发阵容中每个球员的平均击球率。由于市场价格既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又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所以它们并不是完整衡量谁最珍视某个特定物品的指标。
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甚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是它却对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永远比排队更能够把物品分配给最珍视它们的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某些情形中,排队的意愿——为了得到剧院门票或棒球比赛门票——也许要比掏钱的意愿更能表明谁是真的想观看演出或球赛。
为倒票辩护的人抱怨说,排队“偏爱那些最有闲暇时间的人”。 [33]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只是在市场“偏爱最有钱的人”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市场按照顾客购买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而排队则根据排队等候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与排队等候的意愿相比,购买物品的意愿是衡量该物品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更好的尺度。
因此,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有时候,市场确实把物品分配给了最珍视它们的人;而在另一些时候,排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 市场和排队,哪个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乃是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抽象的经济推理就可以事先得到解决的问题。
然而,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还会招致一个更深层的、更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功利主义的考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考量。特定物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价值超出了它们给个体买方和卖方带来的功利。一个物品的分配方式,有可能是使其成为某种物品的因素之一。
下面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纽约公共剧院在夏季免费演出莎翁戏剧的问题。该剧院的发言人在解释剧院为什么反对受雇替人排队这种做法时说,“我们想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但是为什么呢?如果门票被倒卖,免费观剧的体验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呢?当然,对于那些想观看演出却无力购票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验是被剥夺了。但是在这里,受到侵害的不只是公平。当免费的公共戏剧变成了市场中的一件商品的时候,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就丢失了,而这种东西要比那些买不起高价票的人所体验到的失落更重要。
纽约公共剧院把它在户外的免费演出视作公众节日——一种市民的庆典。可以这么说,它是这个城市给自己的一件礼物。当然,观看演出的座位是有限的,整个城市的市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都来观看戏剧。但是剧院的想法是让大家都可以免费地观看莎翁的戏剧,而不考虑其是否具有支付能力。从本应是礼物的活动中收取入场费或允许黄牛倒票,都是有违其初衷的。这种做法把公众节日变成了一笔生意,亦即一种图谋私利的工具。这就好比该城市让人们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付钱观看焰火表演一样。
类似的考量也可以用来解释在国会山付钱雇人排队错在何处。一种反对意见是关于公平的:富有的说客们垄断了国会听证会的市场,从而剥夺了普通民众参加听证会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参加国会听证会的不公平,还不是这种做法唯一令人讨厌之处。假设说客们雇用排队公司的做法会被征税,而且此项收益会被用来使普通民众也能够享受得起其他人替他们排队的服务。这种补贴也许可以采用诸如抵用券的形式,普通民众可以将其拿到排队公司以一定折扣率兑换成现金使用。这种方案也许能够减少现行做法中的不公平成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会招致一个更深层的反对意见:把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件事情变成一种可售商品,是对国会的侮辱和贬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允许人们免费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做法“低估”了国会听证会这一物品的价值,从而导致了排队。替人排队的行业通过确立市场价格的方式修正了这种低效率的状况。它把听证室的座位分配给了愿意出最高价的人,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对代议制这一物品进行估价。
如果我们追问国会为什么一开始就对参加听证会“估价过低”,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假设为了减少国债,国会决定收取听证会门票,比如,1 000美元可以获得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个前排座位。许多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因为入场费对于那些无力购买入场券的人不公平,而且也是因为向公众收取参加国会听证会的费用乃是一种腐败行径。
我们时常把腐败与非法所得联系起来。然而,腐败远不只是指贿赂和非法支付。腐蚀一件物品或者一种社会惯例也是在贬低它,也就是以一种较低的评价方式而不是适合它的评价方式来对待它。国会听证会收取入场费的做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腐败。这种做法把国会看成一种生意,而并非一种代议机构。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回答说,国会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意,因为它常常把影响力和恩惠出售给特殊利益集团。所以,那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点并收取费用呢? 答案是:游说、以权谋私以及内部交易这些已然困扰国会的现象也是各种腐败的实例。它们反映了政府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堕落。在任何对腐败的指控中,都会涉及有关一个机构(此处是国会)所正当追求的目的和目标的观念。在国会山替人排队的生意,亦即游说行业的一种延伸,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腐败。它并不违法,而且付款也是公开进行的,但是它却因为把国会当作了谋获私利的摇钱树而非实现公共善的工具而贬低了国会。
为什么一些付费插队、替人排队和倒票行为会令我们觉得讨厌, 而另一些这样的做法却不会呢? 其原因是市场价值观对某些物品具有腐蚀性,但却适宜于其他一些物品。在我们决定一件物品应当由市场、排队或者其他某种方式来分配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该物品的性质以及人们在评价这件物品时应当采用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由3起“低估”物品而引起倒票的案例:一是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露营地,二是教皇本笃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举行的露天弥撒,最后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现场音乐会。
加利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每年都会吸引至少400万名游客前来。大约有900个主要的露营地可以提前预订,每晚象征性地收取20美元。人们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订,每月15号上午7点钟开始,最早可以提前5个月预订,但仍一票难求。这方面的需求太大, 尤其是夏季,因此在预订刚开始的几分钟内露营地的门票就会被预订一空。
然而,2011年《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的一篇报道称,票贩子以100~150美元一晚的价格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出售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一直禁止倒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接到了如洪水般对黄牛党的投诉,于是它设法制止黄牛党的不正当交易。 [34] 根据规范的市场逻辑,我们不明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国家公园管理局想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为社会提供的福利最大化,那么它就应当使那些最珍视露营体验的人享用这些露营地,而珍视的程度应当根据人们付费的意愿来定。就此而言,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欢迎黄牛党,而不是试图驱逐他们。或者,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把约塞米蒂露营地的门票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的价格,以消除超额需求。
然而,公众对倒卖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的行为十分愤怒,他们拒绝了这种市场逻辑。披露这一事件的《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以“黄牛党侵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吗?”为大字标题,对黄牛党进行了谴责。它把倒票行为视作一种应予以制止的骗局,而不是一项有益于社会功利的服务。这篇社论指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奇观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不只属于那些付得起额外价钱给票贩子的人。” [35]
在人们敌视倒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门票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平,另一种则是关于评价一个国家公园的适当方法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所担忧的是:倒票对于一般收入阶层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无力支付每晚150美元的露营地门票。第二种反对意见隐含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社论所提出的反问中(即“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吗?”);它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东西是不应当拿来估价待售的。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公园不只是使用的对象或社会功利的来源。它们是有着自然奇观和美景、值得人们欣赏甚至敬畏的地方。黄牛党兜售这种地方的门票似乎是对美的一种亵渎。
另一个市场价值观与神圣的事物相冲突的案例是:当教皇本笃十六世首次访问美国时,人们对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露天体育场举办弥撒的门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这些体育场所能够提供的席位数量,甚至扬基体育场也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免费门票通过天主教主教教区和本地教区分发。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倒票行为——一张门票在网上至少卖到200美元。于是,教会官员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其理由是参加宗教仪式的门票不应当被拿来买卖。教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不应当有门票市场。你不能花钱庆祝圣典。” [36]
那些从黄牛手中买到门票的人也许不会赞同这个观点。他们成功地买到了门票并庆祝了圣典。但是我认为,教会那位女发言人所试图表明的乃是一个不尽相同的观点:尽管通过从黄牛手中购票有可能参加教皇的弥撒活动,但是如果这样的体验是可以被待价而沽的话,那么这个圣典的精神也就被玷污了。把宗教仪式或自然奇观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乃是一种大不敬。把圣事变成获利的工具,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但是,当我们碰到部分是商业因素而部分是其他因素的事件时,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2009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他的家乡新泽西州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他把最高票价定为95美元,尽管他本来可以把票价定得更高,而且演出也仍会场场爆满。斯普林斯廷的这一限价行为导致了猖獗的倒票行为,而且也使他损失了一大笔钱。在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最近的巡回演唱会中,最好的座位票已经被卖到了450美元一张。那些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此前演唱会票价的经济学家们发现,由于收取的票价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那一个晚上就损失了约合400万美元的收入。 [37]
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呢? 对于斯普林斯廷而言,保持门票价格相对便宜乃是他对其工薪阶层粉丝恪守承诺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理解自己音乐会的一种方式。诚然,演唱会是用来赚钱的,但赚钱只是一部分。它们还是一个庆祝活动,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广大观众的构成和他们的特征。演唱会不仅由歌曲构成,而且也是由表演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所构成的。
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一篇关于摇滚音乐会经济的文章中,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指出,现场演唱会并不完全是一种商品或市场物品,因而把它们当成商品实在是贬低了它们:“唱片是商品,音乐会则是社交活动;试图把现场体验当作商品,你会产生把这种体验完全毁掉的风险。”他引证阿兰·克鲁格(克鲁格是一名经济学家,曾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演唱会门票的定价方法)的观点说:“摇滚音乐会还具有一种更像是派对而不是商品市场的因素。”克鲁格解释说,斯普林斯廷演唱会的门票不只是一种市场商品,它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礼物。如果斯普林斯廷索取市场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那么他将破坏他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 [38]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公关,是放弃一些眼前收益从而保护声誉并将长期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但这不是理解它的唯一方式。斯普林斯廷可能相信,而且也有理由相信,把他的现场演出当作一种纯粹的市场商品会贬低它,也就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评价它。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与罗马教皇本笃也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我们已经讨论了若干种付费插队的方式:雇人排队、从黄牛手中购票或者直接从诸如机场或游乐场购买插队特权。上述每一种方式都用市场伦理(付钱获取快速服务)取代了排队伦理(依序等候)。
市场和排队——即付费和等候——是两种不同的物品分配方式,而且各自适合不同的事情。排队的伦理“先到先得”有一种平等主义的诉求。它要求我们至少为了某些目的而忽视特权、权力和经济实力。我们像孩子一样被训诫:“依序等候,不要插队。”
这一原则似乎不仅适合于操场和公交车站,也适合于剧院或棒球场的公共厕所。我们厌恶在排队时有人插到我们前面。如果有人因急需而请求插队,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乐意成全他的。但是,如果某个排在队伍后面的人拿10美元与我们调换位置——或者如果管理者在免费厕所旁为富有者(或有急需的顾客)设置快速付费厕所,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种做法很怪异。
但是排队伦理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如果我要出售我的房子,我就没有义务仅仅因为某个报价是第一个向我提出的报价而接受它。出售我的房子和等候公交车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应当遵循不同的规范。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某项原则——无论是排队原则还是付费原则——应当决定对所有物品的分配。
有时候规范会发生变化,而且人们也搞不清楚究竟哪项原则应当处于支配地位。想一想你在打电话给银行、医保机构或有线电视供应商并等候他们接听你的电话时所听到的反复播放的录音信息:“您的电话将按照我们接收到的顺序依次得到应答。”这就是排队伦理的本质。就好像这家公司正在努力地用公平这种香油来舒缓我们的不耐烦似的。
但是不要把那种录音信息太当回事儿。如今,一些人的电话会比另一些人的电话更快接通,你可以把这叫作电话插队。越来越多的银行、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都给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提供特殊的电话号码,或者把他们的电话转接到精英客服中心迅速接听。呼叫中心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能够“分辨”来电,并为那些来自富裕区的电话提供更快捷的服务。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最近提议给经常搭乘飞机的乘客提供一项额外待遇(尽管存有争议):多花5美元就可以与在美国的客服代理人通话,而不是被转接到一个位于印度的呼叫中心。但是达美公司的这项建议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最后只得放弃。 [39]
先接听你最优质(或最有潜力)的客户的电话有什么错吗? 这取决于你售卖的物品的性质。他们打电话来是咨询透支费还是咨询阑尾切除术?
当然,市场和排队并不是唯一的分配物品的方法。一些物品是根据产品优劣进行分配的,另一些物品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还有一些则是根据抽签或运气来进行分配的。大学通常会录取最有天赋和最有潜力的学生,而并不是那些最早提出申请或是为了一个新生名额而付钱最多的学生。医院的急诊室是根据病人病情的紧迫性,而不是根据他们到达的先后时间或他们支付额外费用的意愿来对待病人的。陪审团成员的选择是随机的。如果你被选上,你就不能雇用他人来代替你。
市场取代排队和其他非市场方式来分配物品的趋势,已遍及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在意到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在机场、游乐场、莎士比亚戏剧节、国会听证会、呼叫中心和诊所、免费高速公路和国家公园等场所的大多数付费插队做法,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而在30年前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关注排队或排队伦理在上述方面消失的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市场或市场伦理侵入的并不只是这些地方。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染上毒瘾的母亲生下婴儿。其中的一些婴儿生来就患上了毒瘾,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婴儿都会遭到虐待或遗弃。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是一位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被称作“预防项目”的慈善机构的创建者,她对此提出了一项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如果患上毒瘾的妇女实施节育措施或长时间控制生育,那么她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300美元现金。自她于1997年启动这个项目至今,已有3 000多名妇女接受了她的建议。 [1]
评论家认为这个项目“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是一种“用金钱换节育的贿赂做法”。他们争辩称,用金钱诱惑毒瘾患者使她们放弃生育能力,无异于强迫;当这个项目的目标所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无助妇女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了。评论家抱怨说,金钱并没有帮助接受者戒掉毒瘾,反而是在资助她们吸毒。正如一位该项目的推销员所说的,“不要让怀孕破坏你的毒瘾习惯”。 [2]
哈里斯承认,她的客户大都用那些钱去买更多的毒品了。但是她相信,为了避免孩子生下来就身患毒瘾,这样做只是个很小的代价。一些用节育换现金的妇女实际上已怀孕10多次;很多妇女也已将多个孩子交由他人代养。哈里斯问道:“是什么使得一个妇女的生育权利比一个孩子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更为重要?”当然,她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她和她的丈夫已收养了一位身患毒瘾的洛杉矶妇女所生的4个孩子。“我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婴儿遭受痛苦。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她的毒瘾强加给另一个人。” [3]
2010年,哈里斯把她的这个激励计划带到了英国;但是在那里,这种用金钱换节育的想法遭到了报刊媒体的强烈批判(《每日电讯》上的一篇文章把它称作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同时也遭到了英国医学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大胆的哈里斯还是把她的计划推广到了肯尼亚;在那里,她支付给阳性艾滋病妇女患者每人40美元,要求她们在子宫内安放一种可以长期节制生育的避孕环。在肯尼亚以及哈里斯打算下一步去的南非,卫生部门的官员和人权倡导者们都对她的计划表达了愤慨和反对。 [4]
从市场逻辑的角度看,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项计划会引起人们的愤慨。尽管一些评论家说这项计划让他们想起了纳粹的优生学,但是“金钱换节育的项目”却是私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这里并没有涉及国家问题,而且也没有人是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节育的。一些人争辩称,在那些极需金钱的毒瘾患者可以轻易得到钱的时候,她们并不能进行一种真正自愿的选择。但是哈里斯却对此回应说,如果她们的判断力真的严重受损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她们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呢? [5]
我们可以把这种交易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因为它使双方都获得了益处,并且增加了社会功利。毒瘾患者得到了300美元,交换条件是她放弃生育孩子的能力。通过支付300美元,哈里斯和她的组织得到了这样一个保证,即毒瘾患者不会在未来再生育身患毒瘾的孩子。根据标准的市场逻辑,这种交易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它把物品——在这个事例中是指对身患毒瘾者再生育孩子能力的控制——分配给了那个愿意为此支付最高价格、因而被认为最珍视其价值的人(即哈里斯)。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对此深感愤怒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而它们合在一起共同阐明了市场逻辑的道德局限。一些人批评用金钱换节育的交易是强制性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贿赂。实际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两种反对意见分别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都反对市场侵入它们并不属于的地方。
反对强制的意见所担忧的是,当一个身患毒瘾的妇女同意为了金钱而进行节育的时候,她并不是自由地做出这个选择的。尽管没有人拿枪指着她的头,但是金钱的诱惑却足以让她无法抗拒。由于她身患毒瘾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极为贫困,所以她用节育换取300美元这个选择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做出的。她实际上有可能会因为她的处境而受到强制。当然,人们会对什么诱惑(在什么情形之下)可被等同于强制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于是,为了评估任何市场交易的道德状况,我们就必须追问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市场关系在哪些条件下反映了选择自由,而又在哪些条件下它们施加了高压?
反对贿赂的意见与上面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交易的条件,而是拿来买卖的物品的性质。让我们来看一下一种典型的贿赂个案。如果一个不择手段的人贿赂法官或政府官员以谋取某种不法利益或好处,那么这一不道德的交易就有可能是完全自愿的。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被强迫,而且他们也都得到了好处。人们之所以反对贿赂,并不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腐败行为。腐败就是买卖某种不应当拿来出售的东西(比如,一种偏袒某一方的判决或一种政治影响力)。
我们通常都把腐败/腐蚀(corruption)与人们用不法手段贿赂政府官员的做法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所看到的,腐败还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就一个物品、一个行动或一种社会惯例而言,当我们根据一种比适合它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对待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对它进行腐蚀。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妇女生下孩子是为了把他们卖掉换钱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是对母亲这种身份的腐蚀,因为它把孩子视作一件被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被疼爱的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政治腐败:当一个法官因接受贿赂而做出一项腐败判决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就好像他的司法权力乃是他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公信力。他根据一个比适合于其职责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看待它从而贬低且贬损了它。
这种广义的腐败/腐蚀观念,便是人们把“金钱换节育计划”指责为一种贿赂的原因。那些把这项计划看成是贿赂的人指出,不论这种交易是否是强制性的,它都是一种腐败/腐蚀。而它之所以是一种腐败/腐蚀,其原因就是交易双方——买方(哈利斯)和卖方(毒瘾患者)——都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为所出售的物品(即卖方生育孩子的能力)估价。哈利斯把身患毒瘾和身患艾滋病的妇女视作一台可通过支付货币而使其停止运转的坏了的生育机器。那些接受她要约的人,也默认了那种贬低其自身人格的观点。这就是把哈里斯的做法指责为贿赂的观点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与腐败的法官和政府官员一样,那些为了钱而选择节育的妇女乃是在出售某种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东西。她们把她们的生育能力看成是一种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应当根据负责和关爱的规范而予以实施的能力或禀赋。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类比是有缺陷的。一个接受贿赂而做出腐败判决的法官所出售的乃是某种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因为这种判决并不是他的财产。但是,一个为了金钱而同意节育的妇女所出售的乃是某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即她的生育能力。撇开金钱不谈,如果这个妇女选择节育(或不要小孩),那么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即便是在没有收受贿赂的情形下,一个法官只要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他就是在做错事。一些人还会争辩称,如果一个妇女有权基于她自己的理由放弃生育能力,那么她也就必定有权为了挣钱而这样做。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论点,那么用金钱换节育的交易就不再是贿赂。因此,为了决定一个妇女的生育能力是否应当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物品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物品:我们是否应当把我们的身体视作我们所拥有并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意愿加以使用和处分的所有物,或者说,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某些使用方式是否就等同于自我贬低?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大问题,也可以见之于有关卖淫、代孕妈妈以及买卖精子和卵子的争论中。在我们可以确定市场关系是否适合于这样一些领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样的规范应当用来调控我们的性生活和生育活动。
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喜欢讨论道德问题,至少在他们以经济学家这个身份自居的时候是如此。他们说,他们的工作是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对其进行判断。他们坚持认为,告诉我们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某种活动或者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某种物品,并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价格体系是根据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至于那些偏好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赞赏或者是否适合于某种情势,价格体系一律不予评价。然而,尽管经济学家们极力坚持上述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各种道德问题之中。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另一个原因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理解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在最近几十年里,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思想侵入了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给非经济类物品定价,而哈利斯为节育提供的300美元要约便是这一趋势中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一直在重构其学科,使其变得更加抽象、更具抱负。在过去,经济学家所处理的是一些典型的经济论题——通货膨胀与失业、储蓄与投资、利率与外贸等问题。他们所解释的是国家如何变得更加富有,以及价格体系如何调整五花肉期货和其他商品的供求关系。
然而,最近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他们论辩说,经济学所提供的不仅是一整套有关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洞见,而且也是一门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核心乃是一个简单但却极其重要的观念: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人类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如下假设而得到解释:人们通过衡量他们所具有的各种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并选择一个他们认为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福利或功利的选项来决定做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观念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东西就都有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是明码的,就像汽车、烤面包炉和五花肉的价格一样。或者,这种价格也可以是隐含的,比如性、婚姻、孩子、教育、犯罪、种族歧视、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甚至人的生命。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价格,供需法则都支配着所有这些东西的供给。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在其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一书中,就这个观点提出了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他反对那种陈旧的观念,即经济学是“研究物质商品分配”的学科。他推测说,这种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够久盛不衰,乃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把某些人类行为交由经济学进行‘冷酷’的计算”。贝克试图使我们彻底摆脱这种犹豫不决的状况。 [6]
在贝克看来,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行事,而不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个“被不断使用的”假设,“构成了人类行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在运用这种经济学分析的时候,不用考虑其所分析的是什么物品。它对生死决定以及“选择某种品牌的咖啡”都可以做出解释。它也可以用来分析伴侣的选择和购买一桶油漆。贝克接着指出:“我信奉这样一种立场,即经济学分析是一种可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性分析,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明码标价,是人们经常会做的决策还是难得会做的决策,是大决策还是小决策,是出于情感目的还是机械目的,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是聪明人还是笨人,是病人还是医生,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是老师还是学生。” [7]
贝克并不认为病人和医生、商人和政治家、老师和学生事实上都知道他们的决策是受经济法则支配的。但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往往会无视我们行动的理由而已。“经济学分析并不假设”人们“必然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使福利最大化,或者他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或者如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话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行为的理由。然而,那些对隐含于每一种人类情境中的价格信号有着敏锐眼光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论与物质考量有多么遥远)都可以被解释成和被看成是对成本和收益的一种理性计算。 [8]
贝克通过对结婚和离婚的经济学分析阐明了他的上述主张:
根据经济学分析,当结婚的预期利益高于仍保持单身或再去寻找另一个更合适的对象的预期利益时,一个人会决定结婚。同样,当一个已婚人士重返单身或与另一个人结婚的预期利益高于离婚产生的利益损失(包括因与子女的分离、共同财产的分割、法律诉讼费用等带来的损失)时,他/她会结束自己的婚姻。由于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存在婚姻市场。 [9]
一些人认为,这种计算观把浪漫从婚姻中剔除了出去。他们论辩说,爱情、义务和承诺乃是无法被简化成金钱的理想。他们坚持认为,一桩好的婚姻是无价的,亦即金钱不能购买的某种东西。
在贝克看来,上述看法太过于感情用事,并且阻碍了人们进行明晰的思考。他写道,那些反对经济学分析的人“用一种值得赞赏的聪明机智(如果说得好听一点的话)”把人类行为解释成下述因素所导致的一种凌乱的、无法预见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无知和非理性、价值观及其常常无法解释的变化、习俗和传统、由社会规范促生的某种服从”。贝克几乎无法容忍这种无法预见的结果。他认为,专心致力于收入和价格效应,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10]
人类所有的行动是否都可以用市场这个形象加以理解?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法律学者以及其他论者都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市场这个形象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不仅在学术界,而且也在日常生活中。很显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目睹了社会以市场关系这种形象重塑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衡量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准,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用金钱激励措施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给钱让人节育乃是一个无耻的实例。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都在努力通过用钱来奖励取得好成绩或在统考中取得高分的学生来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在教育改革中,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措施可以解决各种困扰学校教学问题的观念极其凸显,因而令人感到非常担忧。
前些时候,我参观了一所非常好且非常有竞争力的公立中学,它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我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只要学生在他们的成绩单上得到一个A,他们的父母就会用金钱奖励他们。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有点令人震惊。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学校本身也会用金钱来奖励那些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洛杉矶道奇队在那些年里有一个推广计划,即为那些上了荣誉名册的中学生提供免费的门票。对于这样的方案,我们肯定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而且我和我的朋友也都因此观看了不少比赛。但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激励措施;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浪费金钱的无效措施。
现在的情势已经截然不同了。金钱激励措施越来越被认为是改善教学的关键,而对于那些在较差的城镇学校中就读的学生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最近一期《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学校是否应当贿赂孩子?” [11] 一些人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贿赂是否有效。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小罗兰·弗赖尔(Roland Fryer, Jr.)试图找出其中的答案。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贫民区长大;他相信金钱激励措施可以鼓励那些就读于市内学校的孩子。在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在美国最大的几个校区对他的这个观念进行了实验。从2007年开始,他的项目为261所市区学校的孩子支付了630万美元,这些孩子主要是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在每个城市中,他都使用了不同金额额度的激励计划。 [12]
· 在纽约市,参与此项目的学校为那些在统考中成绩优秀的四年级学生每人奖励25美元。七年级学生每次考试优秀者则可获得50美元。七年级平均每个学生可以获得231.55美元。 [13]
· 在华盛顿特区,如果学生按时上课、表现优异并按时完成家庭作业,那么学校就会奖励他们现金。勤奋努力的孩子每两个星期可以攒到100美元。平均每个学生每两个星期可攒到40美元,一学年总共可攒到532.85美元。 [14]
· 在芝加哥,学校会给在课程学习中取得好成绩的九年级学生以现金奖励:成绩为A的学生可得50美元,成绩为B的学生可得35美元,成绩为C的学生可得20美元。成绩最好的学生一学年可积攒到可观的1 875美元。 [15]
· 在达拉斯,二年级的学生每阅读一本书,学校就会奖励他2美元。为了得到现金,学生们必须通过计算机测试以证明他们阅读了那本书。 [16]
奖励现金的做法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在纽约市,用现金奖励统考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的做法,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学业表现。在芝加哥,用现金奖励表现优异学生的做法提高了学生的上课出勤率,但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统考成绩。在华盛顿特区,用现金奖励学生的做法帮助一些学生(拉丁裔美国人、男生和行为有问题的学生)取得了较好的阅读成绩。在达拉斯,用现金奖励学生的计划在二年级学生的身上取得了最好的效果;阅读每本书就可得到2美元的二年级学生,在学年末都取得了较好的阅读理解成绩。 [17]
弗赖尔的计划乃是晚近诸多奖励表现优异学生的计划中的一个。另一个与之类似的计划为那些在高级实习班测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提供现金奖励。高级实习班课程使得高中生有机会去挑战大学水平的数学、历史、科学、英语和其他科目。1996年,得克萨斯州启动了这项高级实习班的激励计划。该计划给通过高级实习班考试(3分或更高分数)的学生奖励100~500美元(这取决于学生所在的学校)。教这些学生的老师也会得到奖励:每一个学生通过考试,老师就可以得到100~500美元,再加上工资津贴。现在,这项激励计划已在得克萨斯州60所高中内实施,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族群的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目前,已有10多个州都已开始用金钱激励措施去奖励那些成功通过高级实习班考试的学生和老师。 [18]
一些激励计划把目标瞄准了老师,而不是学生。尽管教师协会对这种激励计划持谨慎态度,但是因学生学业表现良好而支付老师金钱的观念却在选民、政治家以及某些教育改革者当中极为流行。从2005年开始,丹佛市、纽约市、华盛顿特区、吉尔福德县、北卡罗来纳州和休斯敦的各个校区也都实施了针对老师的金钱激励计划。2006年,美国国会也设立了“教师激励基金”(Teacher Incentive Fund):如果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生取得了好成绩,他们的老师就可以得到现金奖励。奥巴马政府给这个计划又注入了一笔资金。近来,在纳什维尔,一项由私人出资的激励计划给中学数学老师提供了近15 000美元的现金津贴,以提高其学生的考试成绩。 [19]
在纳什维尔,尽管奖金津贴非常高,但对学生的数学成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在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的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多的学生(包括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具有少数族群背景的学生)被激励而参加了高级实习班的课程。很多学生也都通过了使他们有资格申请大学贷款的统考。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这却并不能够证明标准经济学有关金钱激励措施的观点:钱给得越多,学生就会越努力学习,成绩也就会越好。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那些已取得成功的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为学生和老师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现金,它们还改变了校园文化以及学生对待学习成绩的态度。这些计划给老师提供了特殊的培训、实验设备,以及课后和周六有组织的学业辅导。在马萨诸塞州的沃赛斯特(Worcester),有一所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的市区学校,它并不只是向那些预先遴选出来的优秀学生而是向所有的学生开设高级实习班的课程,而且还录取了身穿印有说唱明星头像的广告衫的学生:“参加这类最难的课程对于那些穿着低腰牛仔裤、崇拜像李尔·韦恩(Lil Wayne)这种歌星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酷了。”现在看来,通过年末高级实习班考试就可获得100美元奖励的做法,所激励的与其说是学生对金钱本身的欲求,还不如说是学生对优异表现的欲求。一个成功通过考试的学生告诉《纽约时报》说:“有这笔钱还是不错的,但它对我们还有更多的意义。”该项计划所提供的每周两次的课后辅导以及18个小时的周六班,对学生来讲也是很有助益的。 [20]
当一位经济学家仔细考察得克萨斯州低收入学校所实施的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的时候,他发现了有趣的一点:该项计划在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它的提升方式却是标准的“价格效应”(即你给的钱越多,成绩就会越好)所无法预测的。尽管一些学校给通过高级实习班考试的学生每人100美元,而另一些学校则奖励500美元,但结果却是那些提供较少奖金的学校的学生表现得更好。对该项计划进行研究的基拉波·杰克逊(C. Kirabo Jackson)指出:学生和老师“都没有像收益最大化者那样行事”。 [21]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金钱有一种表现效应(an expressive effect)——使学业成绩变得“很酷”。这正是金钱数量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尽管在大多数学校里,只有英语、数学和科学的高级实习班课程有资格得到现金激励,但是该项计划也使得更多的学生参与了诸如历史和社会研究这样的高级实习班课程。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取得成功的方式,并不是贿赂学生努力学习,而是改变他们对待成绩的态度以及改变校园文化。 [22]
健康保健是另一个广泛运用金钱激励措施的领域。医生、保险公司和雇主都越来越愿意用付钱的方式使人们保持健康——服药、戒烟和减肥。你可能会认为预防疾病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乃是充足的动机。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有1/3到1/2的病人并没有服用医生开具的药物。当这些人病情恶化的时候,从总体上来讲,其结果就是每年要额外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因此,医生和保险公司都在用金钱激励措施来促使病人按照医嘱服药。 [23]
在费城,病人如果服用医生开具的华法林药片(一种防止血栓形成的药片),就可以得到10~100美元不等的奖励。(一个计算机化的药盒会记录他们服药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当天是否获得奖励。)参与该项激励计划的病人如果按照医嘱服药,那么平均每个月可得到90美元的奖励。在英国,一些患有精神分裂或精神疾病的病人,如果可以证明自己每月都按医嘱服用了治疗药片,就可以得到15英镑(约合22美元)的奖励。青春期少女,如果保证接种可防御那种通过性传播的、会引发子宫癌变的病毒的疫苗,就可以得到45英镑(约合68美元)的奖励。 [24]
吸烟给那些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公司增加了高额的成本。于是在2009年,通用电气开始给它的一些戒烟雇员以金钱奖励——如果他们能够戒烟一年,就可以得到750美元的奖励。这项举措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所以通用电气又把这项计划推广到它在美国的所有员工。西夫韦零售连锁商店为那些不抽烟以及那些能够控制体重、血压和胆固醇的员工提供较低的健康保险费。越来越多的公司都通过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激励其员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现在,美国80%的大公司都给那些参与健康计划的人提供金钱奖励。而几乎一半的大公司会因为员工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惩罚他们,特别是要求他们交付更多的健康保险费。 [25]
减肥乃是金钱激励实验最诱人但却不好把控的目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真人秀节目《减肥达人》(the Biggest Loser),就把当前流行的付钱减肥计划搬上了银幕。这个节目为赢得季度减肥幅度最大的冠军奖励25万美元。 [26]
医生、研究人员和雇主也都尝试提供较为适度的激励措施。美国的一项调查报告称,用几百美元的奖金就可以激励肥胖者在4个月之内减掉大约14磅。(遗憾的是,体重减轻被证明只是暂时性的。)在英国,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要花费其预算的5%来应对各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该机构尝试向超肥胖者支付425英镑(约合612美元),以促使他们减肥并在两年内保持不反弹。这项计划被称为“以磅换镑计划”(Pounds for Pounds)。 [27]
我们可以就付钱使人们采取健康行为这件事情提出两个问题:这是否有效?这是否会遭到反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赞同付钱使人们保持健康的实例乃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问题。唯一的真正问题是这些激励计划是否有效。如果金钱能够激励人们按医嘱服药、戒烟或参加体育活动,并因而可以减少此后要支出的高额医疗费用,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反对这些计划呢?
然而,确实有很多人都反对这些计划。用金钱激励措施使人们采取健康行为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争论。一种反对意见是关于公平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关于贿赂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乃是以不同的方式从政治谱系的两端予以阐发的。一些保守主义者论辩说,肥胖者应当自行减肥;花钱(特别是用纳税人的钱)让他们减肥就是用钱来奖励懒惰行为,这是不公平的。这些批评家把金钱激励措施看成是“对放纵行为的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治疗形式”。这种反对意见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都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因此把钱给那些未能自行控制其体重的人乃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这些钱出自国民医疗保健机构的时候(正如英国人有时候做的那样)。“付钱给某人让他戒除坏习惯乃是保姆式国家思维方式的终极形式,因为这种做法会使这些人不用为他们自己的健康承担任何责任”。 [28]
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担忧:用金钱奖励身体健康(以及对身体不健康施以惩罚)的做法,会以不公平的方式使那些无法掌控医疗条件的人处于不利境况之中。允许公司或医疗保险公司在确定保险费的问题上区别对待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的做法,对于那些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使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进而会使他们身处更危险的境地。给每个到体育馆参加锻炼的人打折是一回事,根据很多人都无法控制的健康结果来设定保险费率则是另一回事。 [29]
反对贿赂的意见比较费解。媒体通常都把健康激励措施说成是一种贿赂。但它们真的是贿赂吗?在用金钱换节育的方案中,贿赂是显而易见的。给妇女金钱以使其放弃生育能力,并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个外在的目的——即防止她们生出更多身患毒瘾的孩子。至少在很多情形中,给她们钱是为了让她们去做违背她们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帮助人们戒烟或减肥的金钱激励措施是贿赂。无论金钱激励措施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外在目的(比如,为了减少公司或国民医疗保健机构的医疗费用),它都是在鼓励那些能够改善接受者健康状况的行为。所以,它怎么会是贿赂呢? [30] 或者,我们稍微换个角度来提问:即使健康行为是为了被贿赂的人的利益,为什么贿赂这种指责还是恰当的?
在我看来,这种指责之所以是恰当的,乃是因为我们担心金钱动机会把其他更好的动机排挤掉。就此而言,它是通过下述方式做到的:健康不只是达到正常的胆固醇水平和身体质量指数,它还要求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且用审慎和尊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身体。付钱使人们按医嘱服药的做法,几乎无助于养成这样的态度,甚至还会破坏这些态度。
这是因为贿赂是有操控性的。它们无视说服的作用,并用外在的理由取代内在的理由。“你不是很不在乎戒烟或减肥对你身体的好处吗?那么你就在乎一下吧,因为我会给你750美元。”
健康贿赂诱使我们去做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去做的某件事情。它们诱使我们基于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受骗也是有帮助的。自行戒烟或减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应当超越这种操控。不然,贿赂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习癖。
如果健康贿赂有效,那么那些对它会腐蚀人们对待健康的正确态度的担忧在品格上似乎就过于高尚了。如果金钱可以治愈我们的肥胖症,为什么还要对操控吹毛求疵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恰当地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乃是自我尊重的一部分。另一个回答更具有道德的实践意义:没有维系健康的态度,那么只要激励措施终止,体重就会重新反弹。
这种情形似乎在目前业已调查的付费减肥计划中已经出现。给钱戒烟的情况似乎稍微好些。但是即便最鼓舞人心的调查研究也表明,有将近90%因拿钱而戒除吸烟习惯的烟民,在激励措施终止后的6个月内又重新开始吸烟了。一般来讲,金钱激励措施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比如,医生的一次预约或一次药剂注射——的效果,要比它在改变长期的习惯和行为方面的效果更好。 [31]
如果无法使人们养成维系健康的价值观,那么用钱使他们保持健康的做法就会事与愿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的问题(即“金钱激励措施是否有效?”)与道德学家的问题(即“金钱激励措施是否会引起反对?”)之间的关联就要比初看上去紧密得多。一项激励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目标。而被恰当构想的目标则会涵盖金钱激励措施所腐蚀的一些价值观和态度。
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孩子每写一封感谢信后,都会给他们1美元以示奖励。(我在读这些信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它们是在强迫下写出来的。)这个策略从长远来看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结果有可能证明,这些孩子在写了足够多的感谢信后最终会意识到写这些信的真正目的,因此即使当他们的父亲不再给他们钱作为奖励的时候,他们也会继续在收到礼物时表达感激之情。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他们会吸取错误的教训,认为写感谢信只是一份计酬工作,一种为了得到报酬而要承受的负担。在这种情形下,习惯就不会养成,而且一旦他们的父亲不再给他们钱,他们也就不会再写这样的信了。更为糟糕的是,贿赂会腐蚀他们的道德教育,并会使他们更难以学到感恩这种美德。即使贿赂孩子让他们写感谢信的做法在短期内会增加产出,但是它最终却会失败,因为它给他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评价相关物品的方式。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用金钱奖励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的情形中:为什么不给取得好成绩或读了一本书的孩子以金钱奖励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孩子学习和阅读。金钱奖励便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项激励措施。经济学认为,人们会对各种激励措施做出回应。尽管一些孩子会因为热爱学习而阅读书籍,但其他一些孩子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不把金钱当作进一步的激励措施呢?
结果可能是——正如经济学逻辑所指出的那样——运用两种激励措施要比只运用一种激励措施更有效。但结果也有可能是,金钱激励措施有可能侵损内在的激励措施,从而使孩子们阅读更少的书籍而不是更多的书籍;或者说,使孩子们在短时间内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阅读更多的书籍。
在这种情形中,市场就是一种工具,但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开始只是作为一项市场机制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一项市场规范。人们对此有一个明显的担忧,即金钱激励措施会使孩子们习惯性地把阅读书籍看成是一种赚钱的方式,并由此侵蚀、排挤或腐蚀孩子们对阅读本身的那份热爱。
采用金钱激励措施让人们减肥、读书或节育的做法,不仅反映了经济学分析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该逻辑。当加里·贝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写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计算成本收益这一假设加以解释的时候,他所指的是“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即被认为隐含在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选项和我们所做出的各种选择之中的那种想象价格。因此,比如,当一个人决定维持婚姻而不是离婚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公布任何价格;他所考虑的是离婚的影子价格——即金钱价格和情感价格——并发现离婚的收益并不足以抵偿其成本。
但是,当今盛行的那些金钱激励计划要比这走得更远。通过给那些不以物质追求为目的的活动确定一种实在且明确的价格,这些金钱激励计划把贝克的影子价格从背后拽了出来,并把它们变成了真实的价格。它们把贝克有关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市场关系的建言付诸实施。
贝克本人据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建议,亦即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人们在移民政策上存在的激烈争论:美国应当取消其由配额、积分系统、家庭偏好以及排队等候等构成的复杂制度,只需要出售移民权即可。考虑到需求,贝克建议把准入价格确定为5万美元或者更高。 [32]
贝克推论说,愿意支付大笔移民费用的移民自然会有许多理想的特征。他们可能年轻、有技术、有抱负、勤劳,并且不可能申请救济金或失业津贴。当贝克在1987年最初建议出售移民权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太难以置信了。但是,对于那些专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用市场逻辑来解决棘手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决定哪些移民可获准进入美国?)的一种明智的甚至是显见不争的方式。
另一位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大约在同时提出了一种与贝克类似的建议。他建议每年设定一个移民准入配额,并把这些准入配额公开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拍者,直至额满为止。西蒙论证说,出售移民权是公平的,“因为它是根据市场导向的社会的标准——即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标准——来区别对待需求者的”。针对那种认为他的计划有可能只让富人移民美国的反对观点,西蒙回应说:可以允许胜出的竞拍者先从政府那里借贷一部分准入费用,并在之后用他们的所得税偿还这笔借款。他指出,如果他们无力偿还,那么可以随时把他们驱逐出境。 [33]
出售移民权的想法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一个市场信念不断高涨的时代,贝克–西蒙规划的主旨很快就被写进了法律。1990年,美国国会规定,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与他的家庭一起移民美国两年;两年以后,如果这项投资创造了至少10个就业岗位,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绿卡)。用金钱换绿卡的计划在终极意义上是一项插队方案,亦即一条获得美国公民资格的快速通道。2011年,两位参议员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用一种类似的金钱激励方式来繁荣受金融危机影响仍处于低迷状态的高端房地产市场。任何购买一幢价值50万美元住宅的外国人都可以得到一种签证,允许他及其配偶、子女在拥有这处房产的前提下一直居住在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用一个大标题概括了这种交易:“买房子,拿签证。” [34]
贝克甚至提议向躲避迫害的避难者收取费用。他宣称,自由市场会使人们很容易就决定应当接受哪些避难者——即那些有充分理由支付费用的人:“很显然,政治避难者以及那些在本国受到迫害的人,为了被准许进入一个自由国家,是会愿意支付一大笔费用的。因此,只要设立一个收费系统,自然就可以避免举行那些浪费时间的听证会,来讨论避难者一旦被强制送回他的国家是否真的会受到身体上的威胁的问题。” [35]
要求一个躲避迫害的避难者支付5万美元的做法,不仅会使你觉得太不近人情,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未对愿意支付费用与有能力支付费用这两点做出区分的另一个例子。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用市场手段解决避难者问题的建议,这是一个无须避难者自掏腰包的建议。法学教授彼得·舒克(Peter Schuck)提出了如下建议:
让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国民财富的水平给每个国家设定一个年度避难者的配额。然后让这些国家在它们之间买卖这些义务。因此,比如,如果日本根据分配方案每年要接收2万名避难者,而它又不想接收他们,那么它可以付钱给俄罗斯或乌干达让它们接收这些避难者。根据规范的市场逻辑,这种情形会使每一方都获益。俄罗斯或乌干达得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收入来源,日本通过外包方式履行了它接收避难者的义务,而且更多的避难者也得到了救助。 [36]
这种避难者市场有点令人讨厌,尽管它使更多的避难者找到了避难之所。但是,它究竟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避难者市场改变了我们有关谁是避难者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的看法。它鼓励参与者——购买者、出售者以及那些拥有可以拿来讨价还价的避难所的国家——把避难者看成是一个要甩掉的包袱或是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一些身处险境的人。
人们可能会承认避难者市场确有贬低人格的作用,可是他们仍得出结论认为,这项计划所带来的是更多的好处而不是伤害。但这个事例却表明,市场不只是一种机制。它们体现了某些规范。它们预设(并促进)了评价所交易物品的某些方式。
经济学家往往假定,市场并不会触及或腐蚀它们所调节的那些物品。但这并非事实真相。市场把它们的印记镌刻在社会规范之上。市场激励措施往往会侵蚀或排挤掉非市场激励措施。
一项有关以色列某些托儿所的研究表明了上述情况是如何可能发生的。这些托儿所面临着一个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一些家长有时候无法按时去接他们的孩子。一位老师在迟到的家长来接孩子之前不得不留下来陪孩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托儿所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金。你猜想一下会发生什么?结果,迟接孩子的现象实际上反而越来越多了。 [37]
如果你现在还假定人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那么这就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结果。你可能会预期,设定罚金会减少而不会增加迟接孩子的现象。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引入金钱惩罚机制的做法,改变了原有的规范。之前,迟到的家长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给老师带来了麻烦。而现在,家长们则把迟接孩子看成是一项他们愿意为之付钱的服务。他们把罚金看成是一项费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强迫老师延长工作时间,而只是用付钱给她们的方式让她们延长工作时间而已。
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何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罚金所表达的是道德上的责难,而费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断的价格。当我们对乱丢废物的人科以罚金的时候,我们是说:乱丢废物是错误的。把啤酒罐随手丢进大峡谷(Grand Canyon),不仅要科以清理费用,而且也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不予鼓励的一种恶劣态度。假设这种行为的罚金是100美元,而且一个富有的徒步旅行者认为,为了不用拿着空罐子出公园这一便利,花这么多钱是值得的。他把罚金看作一种费用,因而把啤酒罐随意丢进大峡谷。尽管他付了罚款,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他做错了事。由于他把大峡谷看成是一个昂贵的垃圾丢弃站,所以他的这种观点表明,他没有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去理解它。
或者,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门留给残疾人使用的停车位的问题。假设一个忙着要去签约的健康人想在其建筑工地附近的地方停车。为了把车停在专门留给残疾人的地方这一便利,他愿意支付一笔颇为高额的罚款,因为他把这笔罚金视作做生意的一种成本。尽管他付了罚款,难道我们就会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错吗?他对待罚金的态度,就好像它是一笔昂贵的停车费用。但是,这里丢失了其间的道德意义。由于他把罚金看成是一笔费用,所以他既没有尊重残疾人的需求,也没有尊重社会通过留出停车空位而方便残疾人的欲求。
当人们把罚金视作一种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鄙视罚金所表达的那些规范。社会对此常常都会予以回击。一些富裕的驾驶者把超速罚单看作他们为了随意飙车而支付的费用。在芬兰,法律明确规定罚款金额以肇事者的收入为基础,并以此反对上述那种思维方式(和驾驶方式)。2003年,尤西·萨洛诺亚(Jussi Salonoja),一位27岁的香肠业继承人,因为在限速每小时40公里的路段上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而被罚款17万欧元(当时约合21.7万美元)。萨洛诺亚是芬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年收入高达700万欧元。此前,最昂贵的超速罚单纪录是由诺基亚移动公司的一位主管安西·万约基(Anssi Vanjoki)创下的。2002年,他因驾驶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在赫尔辛基超速行驶而被罚款11.6万欧元。当万约基事后证明其收入因诺基亚公司利润缩水而被减少之后,法官才降低了罚款数额。 [38]
芬兰人的这张超速罚单之所以是罚金而不是费用,不只是因为它们根据收入进行浮动这个事实,而是因为隐含在其背后的道德谴责,亦即违反限速规定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累进所得税也根据收入浮动,但它们却不是罚金;它们的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税收,而不是一种通过惩罚来创收的活动。芬兰所开出的这张21.7万美元的超速罚单表明,社会不仅希望违法者能够支付危险行为的成本,而且也希望惩罚与罪责相符合——以及与违法者的银行存款余额相符合。
尽管一些有钱的超速驾驶者对待限速问题态度傲慢,但是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却是无法轻易消除的。在大多数情形下,被叫停在路边并被开具超速罚单仍带有一种耻辱的味道。没有人会认为警察只是在收取道路费,或是在给超速者开具一张可方便他快速往返的账单。近来,我偶然看到了一则怪诞的建议,它通过表明超速费用(而不是罚金)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阐明了这个问题。
尤金·“吉诺”·迪斯莫内(Eugene “Gino” Disimone)是一名竞选内华达州州长的独立候选人。他在2010年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州预算的方案:允许人们在支付25美元(每天)后超速行驶,并在内华达州指定的路段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行驶。如果你想不定时地选择提速驾驶,那么你可以买一个应答器,并在你需要开得快些的时候用手机拨打你的账号。只要从你的信用卡中扣除了25美元,那么你就可以在未来的24小时内自由地快速行驶,而不会被警察拦下停在路边。如果一个警察用测速雷达枪发现了你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那么你的应答器就会发出信号,表明你是一位付费的消费者,因而也就不会被开具任何罚单。迪斯莫内估计,他的这个建议可以在不提高税收的情形下每年至少为该州增加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尽管这对于该州的预算来说是一笔非常诱人的意外之财,但是内华达州高速公路巡警却说,这项计划会危害公共安全,而且该候选人在竞选中也肯定会落选。 [39]
在实践中,罚金和费用之间的区别有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有争议的。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你在乘坐巴黎地铁的时候没有购买2美元的车票,那么你就会被罚款60美元。这项罚款乃是对那种用逃票的方式欺骗地铁系统的做法的一种惩罚。然而,一群专门逃票的人最近想出了一种把罚金转变为费用的聪明方法,不过这也是一种很平常的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保险基金,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被抓到,该基金就会为他支付罚款。每个成员每月给该项基金(逃票者互济会)缴纳大约8.5美元的费用,而这笔钱远比购买一张合法的月票所需花费的74美元要便宜得多。
这个互济会的成员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金钱,而是对免费开放公共交通的一种意识形态承诺。这个群体的一位领导者告诉《洛杉矶时报》说:“这是一种集体抵抗的方式。在法国,有些事情(上学和健康)应当是免费的。那么为什么公共交通不免费呢?”尽管逃票的人不会很多,但是他们的全新计划却把对欺骗科处的罚金变成了一种月度保险费,一种他们为了抵抗交通收费系统而愿意支付的价格。 [40]
为了确定是罚金合适还是费用合适,我们就必须弄清楚相关社会制度的目的以及应当调整它的那些规范。答案会因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讨论的是晚到托儿所接孩子以及巴黎地铁逃票的问题,还是逾期把DVD还给当地音响商店的问题。
在音响商店初创的岁月,它们把因迟还录像带而交付的费用看作是罚金。如果我迟还了录像带,营业员就会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态度。好像我迟还3天电影录像带,就是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似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有点错位。一个商业性音响商店毕竟不是公共图书馆。对于那些没有按时归还图书的人,公共图书馆所科处的不是费用,而是罚金。这是因为公共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共同体中组织人们免费分享书籍。所以,当我悄悄地把已过借阅期的书还给图书馆的时候,理应感到内疚。
但音响商店做的是生意,其目的就是通过出租录像带赚钱。所以,如果我没有按时归还电影录像带并付费多借了几天,那么我应当被看成是一个较好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较差的消费者。或者,我理应这么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方面的规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音响商店似乎已不再把逾期不还而缴纳的钱看成是一种罚金,而是看成一种费用。
在通常情况下,道德要求会更高些。让我们来看看人们就罚金和费用之间偶尔出现的模糊界限展开的争论:在中国,因违反政府独生子女政策而被科处的罚款,在富裕的人眼中越来越被看作是生育第二个孩子所要支付的一笔费用。这项为了减缓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而在30多年前就已经实施的政策,使得城市中的大多数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如果农村家庭第一胎生育的是女孩,则被允许生第二胎。)罚款金额因地而异,但在大城市中,罚金已高达20万元人民币(约合3.1万美元);这对于工薪阶层来讲是一笔很大的数额,但对于富裕的企业家、体育明星和社会名流来讲则是微不足道的。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的一则报道指出,广州的一位孕妇和她的丈夫“趾高气扬地”步入当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把一沓钱扔在桌子上说:“这是20万。我们要照顾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41]
计划生育官员试图通过以下做法来重申此项举措的惩罚性质:增加富裕超生者的罚金,公开谴责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名流并禁止他们上电视,以及不让超生的企业老总得到政府的合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翟振武解释说:“对于富人来讲,罚金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必须在真正可以打疼他们的地方——如名誉、声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更重地打击他们。” [42]
政府当局把罚金看成一种刑罚,并希望它还能产生一种耻辱感。它们不想把它变成一种费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担心富裕的家庭会生育太多的孩子。富裕超生者的数量相对来讲是很小的。问题的关键乃是构成独生子女政策之基础的规范。如果这里的罚金只是一种费用的话,那么国家就会陷于一种尴尬的交易之中,因为它在向那些有能力和有意愿支付超生费用的人出售超生权。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呼吁采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控制人口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与中国官员竭力避免的那种以费用为基础的计划生育体系极其相似。这些经济学家敦促那些需要限制人口数量的国家发放可交易的生育许可证。1964年,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就提出了一个可交易的生育准许体系,作为处理人口过剩问题的一种方式。每个妇女都可以得到一张授权她们生育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这取决于政策的规定)的准生证。她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种准生证或根据现行价格把它卖掉。博尔丁设想了这样一种市场,其间,那些渴望拥有孩子的人可以从(他以一种粗鲁的方式所说的)“穷人、修女、未婚妇女等诸如此类的人”那里购买准生证。 [43]
这项计划要比固定配额体系(如独生子女政策)少一些强制性。同时,它在经济上也更有效,因为它会把物品(在这个情形中就是指孩子)分配给最愿意为它们支付金钱的消费者。近来,两位比利时经济学家又重申了博尔丁的建议。他们指出,由于富人有可能会愿意从穷人那里购买生育许可证,所以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给穷人增加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来减少不平等现象。 [44]
一些人反对对生育作任何限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为了避免人口过剩,对生育权进行限制是合法的。让我们暂时撇开有关原则的争论,而设想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决定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下述两项政策中哪项政策会较少招致人们的反对:是(1)一个固定配额的体系,它限制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并对超生者科处罚款;还是(2)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它给每对夫妻发放一张可交易的、授权持有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准生证?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上述第二项政策显然更为可取。如果让人们在使用准生证抑或出售准生证的问题上拥有选择的自由,那可以使相关的人都获益,而同时也不会使任何人受损。那些买卖准生证的人(通过相互获益的交易)获得了好处,而那些没有进入这个市场的人的境况也并不会比他们如果处在固定配额体系下的境况更糟,因为他们仍可以生育一个孩子。
然而,就人们可以买卖生育权的那种体系而言,存在着某种让人感到担忧的方面。部分担忧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这样一种体系是不公平的。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当成一种只有富人负担得起、穷人却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如果生育孩子是人类繁盛的一个核心要素的话,那么把生育孩子的条件限定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就是不公平的。
除了上述基于公平这个理由的反对意见以外,另一种反对意见还认为它是一种贿赂。这种市场交易的核心要素乃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活动:希望多要一个孩子的父母肯定会引诱或诱使其他有可能成为父母的人出售他们的生育权。从道德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购买一对夫妻生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经济学家们有可能论辩说,孩子市场或生育权市场拥有一种有效的德性:它把孩子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而衡量标准便是支付能力。但是,交易生育权的做法促使人们用一种商业态度去对待孩子,而这种态度则会腐蚀父母的品格。处于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之核心地位的乃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的孩子是不可转让的,把他们拿来买卖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从另一对可能成为父母的人那里购买一个孩子或购买生育一个孩子的权利,就是在腐蚀父母品格本身。如果你通过贿赂其他夫妻不要孩子而自己生育了孩子,那么爱你的孩子这种经验难道就没有被败坏吗?你是否有可能至少在诱惑下向你的孩子隐瞒这个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不论生育许可证市场有多少好处,它都会以固定配额体系不会采用的方式腐蚀父母的品格,尽管固定配额体系也非常令人讨厌。
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也与有关如何减少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的争论相关。政府应当给排放设定一个限度并对那些超标排放的公司科以罚金?还是应当提供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第二种方案的意思大致是说,与丢弃废品不同,排放乃是做生意所要花费的一种成本。但这是否正确呢?或者说,向空气中排放过量废气的那些公司是否应当受到某种道德上的谴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计算成本和收益,而且还必须决定我们想提倡的究竟是哪种对待环境的态度。
在1997年举行的京都会议(Kyoto conference)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一种强制性的全球排放标准都必须包括一个交易方案,允许各个国家买卖排放权。所以,比如,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框架下,美国可以通过要么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要么支付费用让其他地方减少排放来履行它的义务。它可以支付费用来重新修复亚马孙雨林或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老旧的煤炭工厂现代化,而不用向国内那些狂吸新鲜空气的悍马车征税。
当时,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特稿的时候就反对这项交易方案。我担心,允许国家购买排放权就好像允许人们付费乱丢垃圾一样。我们应当竭力强化而不是弱化破坏环境所应背负的道德耻辱。与此同时,我还担心,如果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花钱来免除他们所负担的减少他们自己国家排放量的义务,那么我们就会侵蚀我们未来在环境问题上展开全球合作所必需的那种共同牺牲的意识。 [45]
针对我的文章,《纽约时报》收到了潮水般的严苛批评信件或挑剔信件——大多数来自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还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市场的德性、交易的有效性或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理。 [46] 在这些潮水般的批评中,我从我原来就读的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表示同情的电邮。他写道,他理解我努力阐述的要点。但他也请我帮个小忙,即是否可以不公开曾经教过我经济学的那个人的身份?
自此以后,我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有关买卖排放权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尽管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些教条式理由。与把垃圾从车窗扔到高速公路上不同,排放二氧化碳本身没有什么可予以反驳的。我们所有的人每次呼吸的时候都在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人们所要反对的是过量排放,亦即一种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支撑此种生活方式的态度,乃是我们应当不予鼓励甚至应当予以蔑视的。 [47]
减少排放的一种方式便是政府管制:要求汽车制造商达到更高的排放标准;禁止化工厂和造纸厂把含有毒素的水排进河道;要求工厂在他们的烟囱上安装过滤器。如果这些公司没有遵守这些标准,就对它们科以罚款。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代环境法实施期间就是这么做的。 [48] 这些以罚款为后盾的管制措施,是一种要求公司为它们的排放行为付钱的方式。这些管制措施也带有道德含义:“我们应当为自己把污水排进小溪和河道而感到羞愧,也应当为自己排放废气从而污染空气而感到羞愧。这不仅有害我们的健康,而且我们也绝不能这样对待地球。”
一些人反对上述管制措施,因为他们不喜欢任何一种让各个行业承担更高成本的做法。但是,另一些对环境保护持同情态度的人却在寻求一些更有效的达到其目的的方式。随着市场声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不断提升,随着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环保倡导者也开始赞同某些基于市场的拯救地球的方式。他们指出,不要给每个工厂都强行设定排放标准;相反,我们只要给排放设定一个价格,而其他的事情就留给市场去解决。 [49]
给排放定价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向它征税。向排放征税可以被视作一种费用而不是一种罚款;但是如果征税足够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使排放者为它们造成的损害付出金钱的代价。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要落实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很难的。所以,政策制定者们采纳了一种更加亲市场的解决排放方案——排放交易。
1990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把一项旨在减少酸雨(它是由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的)的计划签署成了法令。这项法令没有给每个电厂设定固定的排放限额,而是给每个公共电力公司发放一张排放一定废气的许可证,然后允许这些公司彼此之间买卖这些许可证。因此,一家电力公司要么减少它自己的排放量,要么从某家其他成功减少排放量的电力公司那里购买额外的排污许可证。 [50]
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因而这一交易方案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 [51] 后来,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全球变暖问题。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它们要么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要么付钱给其他国家让它们减少排放。实施此项方案的理由乃是它减少了遵守条款的成本。如果替换印度农村使用的煤油灯要比减少美国的碳排放便宜,那么为什么不让美国出钱来换掉那些煤油灯呢?
尽管有这样的诱惑,但美国还是没有加入《京都协议》,而此举使得随后的全球气候谈判搁浅。不过,我的兴趣与其说是协议本身,不如说是它们是如何表明全球排放权市场的道德成本的。
就一些人所建议的生育许可证市场而言,其道德问题在于该体系促使一些夫妻贿赂其他人以使他们放弃生育孩子的机会。这个体系经由鼓励父母把孩子视作可转让的、可买卖的商品而侵蚀了父母之爱的规范。全球排放许可证市场中的道德问题则与上述道德问题不同。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贿赂,而在于它把义务外包给了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在全球背景下要比在国内情势中更为尖锐。
就全球合作而言,允许富裕的国家通过从其他国家那里购买排放权(或资助那些能够使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的项目)而使它们在能源使用方面不做实质性减排的做法,确实侵损了下面两项规范:它不仅对自然确立了一种工具性态度,而且还破坏了那种对于创建一种全球环境伦理来讲所必要的共同牺牲精神。如果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花钱来免除它们所负担的减少自己碳排放的义务,那么这就与上文所述的大峡谷徒步旅行者的例子有些相像。只是现在,富有的徒步旅行者可以在扔啤酒罐以后不用接受罚款的惩罚,只要他雇人去清理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垃圾即可。
的确,这两个例子并不完全相同。随意丢弃垃圾要比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少的替代性。丢弃在大峡谷的啤酒罐并不能用远在离大峡谷半个地球之远的一块原始土地来补偿。与之不同的是,全球变暖乃是一种累积性的危害。就整个天空而言,地球上哪些地方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哪些地方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道德和政治上讲,这却事关重大。让富裕的国家通过花钱而使其不必改变它们浪费资源的习惯,会强化一种错误的态度——即认为自然是那些能够负担费用的国家可随意倾倒垃圾的地方。经济学家常常假设,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就是一个设计一种正确的激励结构并让各个国家签字同意它的问题。但是这种假设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要点:规范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全球行动,要求我们找到一种建构某种新环境伦理(即一整套新的对待我们所共享的自然世界的态度)的方法。一个全球的排放权市场,无论其有多高效,都会使我们更难培养起一种负责任的环境伦理所要求的节制和共同牺牲的习惯。
自愿碳补偿行动的日益增多,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现在让消费者交付一定的费用来抵消其个人对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影响。英国石油公司的网站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网页,消费者可以去那里计算他们的驾驶习惯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并且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某项绿色能源计划去补偿他们个人的废气排放。根据该网站的说法,平均每个英国驾驶员每年的排放量,大约可用20英镑去补偿。英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种相同的估算方案。只要支付16.73美元,你就可以补偿你在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往返旅行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航空公司会把你交的16.73美元资助给内蒙古的一家风力农场,以弥补你的飞行给天空造成的损害。 [52]
碳补偿行动反映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想法:为我们因使用能源而给地球造成的损害定一个价格,并通过逐人依此价格付钱的方式使其排放变得正当。设立基金以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植树造林和清洁能源的计划,当然是值得的。但是这种补偿行动也产生了一个危险:那些购买排放权的人会认为他们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一种进一步促使气候变化的责任。这里的危险在于:至少对某些人来讲,碳补偿行动会成为一种相当轻松的机制:我们只需要付钱,就无须对我们原有的习惯、态度和生活方式做出更为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于解决气候问题来说可能是必需的。 [53]
碳补偿行动的批评者把它们类比成赎罪,即有罪的人用付钱给教会的方式来补偿他们的罪过。网址为www.cheatneutral.com的网站对碳补偿行动进行讥讽,把补偿买卖说成是一种不忠行为。如果生活在伦敦的某个人因出轨而感到内疚,那么他就可以付钱给曼彻斯特的某个人要他对家庭保持忠诚,以此来“补偿”他的罪过。这个道德类比并不完全恰当:对感情的不忠并不是因为它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幸总量而遭到反对;它是对某个特定的人所犯的错误,因而是无法通过在其他地方做某种有德的事情而可以变得正确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碳排放并不是这种错误,而是一种累积性的错误。 [54]
批评者们仍言之有理。将排放温室气体的责任商品化和个体化,可能会引发与上面那个日托幼儿园的例子(向迟接孩子的家长收费,结果迟到的家长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一样的困境。一如我们所知:在全球变暖的时代,驾驶一辆悍马车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贪得无厌、自我堕落的浪费的象征。与之相反,混合动力汽车则有着某种特定的声望。但是,碳补偿行动却会因为给排放赋予了某种道德许可而可能会破坏这些规范。如果悍马车的车主可以通过向一个在巴西植树造林的组织开具支票而减轻自己心中的内疚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把他们大排量的汽车换成一辆混合动力汽车。从表面上看,悍马车拥有者们开具支票的举动似乎是令人尊重的,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这样下去,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广泛的集体回应的压力也会由此减弱。
当然,我所描述的这个情景乃是虚构的。罚金、费用以及其他金钱激励措施对规范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能得到准确的预测,而且还会因为情形的不同而不同。我的看法是:市场反映并推广了某些规范,即评价所交易物品的某些特定的方式。因此,在决定是否要将某种物品商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效率和分配公平,我们还必须追问这些市场规范是否会排挤掉非市场规范,而且如果会的话,那么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得不偿失。
我并不是在宣称,促进人们对环境、养育孩子以及教育保有有德行的态度,肯定永远都优于其他因素的考量。贿赂有时候也会发挥作用,而且在某些场合贿赂还是有道理的。如果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钱让他们读书,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的阅读技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决定尝试这么做,以期教会他们在以后也热爱学习。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贿赂行为(即一种在道德上有所妥协的做法)乃是在用一种较低的规范(为赚钱而读书)取代一种较高的规范(因为爱读书而读书)。
随着市场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侵入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健康、教育、生育、难民政策、环境保护等领域,上述困境出现得更为频繁了。当经济效率或经济增长的承诺意味着要给我们认为无价的物品定价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当我们在决定是否要进入存在道德问题的市场以期实现一些有价值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左右为难。
假设我们的目的是要保护濒危物种,比如黑犀牛。从1970年到1992年,非洲的黑犀牛数量从6.5万头减少到了2 500头以下。尽管猎杀濒危物种是非法的,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却依旧无力保护黑犀牛免遭偷猎者的射杀,这些偷猎者在亚洲和中东卖掉犀牛角以获取高额利润。 [55]
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南非保护生物多样性机构的官员开始考虑用市场激励措施来保护濒危物种。如果允许私人农场主可以把射杀数量有限的黑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那么农场主就有动机去饲养黑犀牛、照顾黑犀牛并阻止偷猎者的捕杀。
2004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批准南非政府许可猎杀5头黑犀牛。黑犀牛是一种极其危险且很难射杀的动物,因而猎杀者都非常珍视猎杀一头黑犀牛的机会。数十年里的首次合法猎杀被要求支付一大笔钱:15万美元;后来,一位美国银行业的狩猎者支付了这笔费用。此后的消费者还包括一位俄罗斯的石油大亨,他付费射杀了3头黑犀牛。
市场解决方案似乎是有效的。在肯尼亚,猎杀犀牛仍然是被禁止的;由于土地上的原生植物被清除并被用来农耕和畜牧,黑犀牛的数量已从2万头减少到了大约600头。然而在南非,由于土地所有者现在因为有了金钱激励而愿意把大量牧场空出来饲养野生动物,黑犀牛的数量开始回升。
就那些不为运动狩猎所困扰的人而言,出售射杀黑犀牛的权利乃是一种用市场激励措施去拯救某种濒危物种的明智方法。如果捕猎者愿意支付15万美元去猎杀一头犀牛,那么农场主就有动力去养殖犀牛并保护它们,并由此增加供给。这是一种有着双重效果的生态旅游:“来付费射杀一头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你不仅能得到一种难忘的经验,同时也能保护黑犀牛。”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市场解决方法似乎是一种不争的胜者。它使一些人获益,但却没使任何人亏损。农场主赚了钱,捕猎者有机会去大胆地捕杀危险动物,而且濒危物种又重新从灭绝的边缘回到了正常状态。谁还会抱怨呢?
当然,这取决于运动狩猎的道德地位。如果你认为为了运动而杀害野生动物在道德上是应予以反对的,那么犀牛狩猎市场就是一种邪恶的交易,是一种道德勒索。你可能会因为这种做法对保护犀牛有好处而表示赞赏,但却会对如下事实予以谴责,亦即这个结果是通过迎合你所认为的富有狩猎者的邪恶快感而达到的。这就好比为了拯救原始的红杉森林免遭破坏而允许伐木工人向富有的捐款人出售砍伐某些红杉树的权利。
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你可能会基于如下理由而反对市场解决方法,即运动狩猎的道德丑态超过了保护犀牛而获得的利益。或者,你有可能决定支付道德勒索费用并出售猎杀犀牛的权利,以期拯救濒危物种。正确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它所承诺的利益。但是,它也取决于运动狩猎者把野生动物当作运动的对象来看待是否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是错误的话,那么它就取决于这个错误的道德意义。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如果没有道德逻辑,市场逻辑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不解决有关恰当评价买卖射杀犀牛权利的道德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这种权利是否应当拿来买卖。当然,这是一个纷争不止的问题。但是,赞同市场解决方法的理据是不能与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评价我们所交易的物品的正确方式的问题——分割开来的。
巨兽猎人在本能上会理解个中要点。他们明白,其运动(以及付费猎杀犀牛)的道德合法性取决于某种特定的有关正确看待野生动物的观点。一些运动狩猎者宣称他们崇敬他们的猎物,并主张射杀一头猛兽乃是尊重它的一种方式。一个在2007年付费猎杀一头黑犀牛的俄罗斯商人说:“我之所以猎杀黑犀牛,乃是因为这是我能给予黑犀牛的最高敬意之一。” [56] 批评者说,射杀生物乃是崇拜它的一种古怪方式。运动狩猎是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评价野生动物,乃是一个处于该争论核心地位的道德问题。它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态度和规范的问题:是否应当创建一个猎杀濒危物种的市场,不仅取决于它是否会增加它们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表达和促进了一种正确评价它们的方式。
黑犀牛市场之所以具有复杂的道德面貌,乃是因为它试图通过推广一些有问题的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来保护濒危物种。下面是另一个狩猎的例子,它给市场逻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
几个世纪以来,大西洋的海象就像美国西部的野牛一样遍布加拿大的北极地区。由于海生哺乳动物的肉、皮、油脂以及乳白色的牙齿都非常珍贵,所以对于狩猎者而言,这些毫无保护的大量海生哺乳动物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猎物。因此,到了19世纪末,其数量已大量减少。1928年,加拿大开始禁止猎杀海象,但是因纽特人除外,因为作为土著狩猎者,在长达4 500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狩猎海象。 [57]
20世纪90年代,因纽特人的头领们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允许因纽特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些海象配额的射杀权利出售给巨兽猎人?这样做,被射杀的海象数量与之前并没有发生改变。因纽特人可以收取这笔狩猎费用,用它来指导运动狩猎者、监督他们的捕杀,并像他们过去做的那样保留海象的肉和皮。这项计划可以改善一个贫穷部落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捕杀的海象也不会超过现有规定的捕杀配额。加拿大政府后来同意了这个建议。
今天,世界各地富有的运动狩猎者都跑到北极,希望有机会射杀一头海象。他们支付6 000~6 500美元以期获得这样的特权。他们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体验追逐一头野兽而带来的刺激,也不是为了体验追逐一个很难捕捉的猎物而带来的挑战。海象不是一种危险动物,它们移动缓慢,绝不是拿枪的狩猎者的对手。在《纽约时代杂志》的一则引人入胜的描述中,奇弗斯把在因纽特人监督之下的海象狩猎比作“长途跋涉后去射杀一个庞大的豆袋椅”。 [58]
向导们把船只驶到距海象15码的范围内,并告诉狩猎者何时射击。奇弗斯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场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运动狩猎者参与了一场射杀猎物的游戏,“子弹正中巨兽的颈部,它的头一晃便倒了下去。鲜血从弹孔中喷涌而出,巨兽不再动弹了。‘狩猎者’放下他的枪,举起相机进行拍摄。”接着,因纽特人开始艰难地工作:把死海象拖上浮冰,把皮和肉切割开来。
这样一种狩猎的吸引力是很难理解的。它没有任何挑战,更像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旅行,而不是一项运动。狩猎者甚至不能把猎物的肉和皮作为奖品带回家。海象在美国是受保护的,因此把它的身体部位带回美国是违法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射杀海象呢?显然,这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射杀“狩猎俱乐部”所提供的狩猎单上的某个物种,比如,非洲的“五巨兽”(豹子、狮子、大象、犀牛和南非水牛)或北极的“大满贯”(驯鹿、麝香牛、北极熊和海象)。
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很多人对此都很反感。但是请记住,市场并不会对它们所满足的各种欲望做出道德价值判断。事实上,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允许因纽特人出售他们所拥有的射杀一定数量海象的权利有很多好处。因纽特人有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而且“名册上的狩猎者”也得到了完成射杀其狩猎单上的野兽的机会,而又没有超出现行规定的捕杀配额。在这个意义上,出售射杀海象的权利就与出售生育权或排放权一样。一旦你拥有一个配额,市场逻辑就会告诉我们,允许交易的许可证可以提高公共福利。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可以使一些人获益。
然而,就射杀海象市场而言,还存在着人们颇有分歧的道德问题。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假设,允许因纽特人继续他们长达数个世纪的猎杀海象的生存方式是合理的。但是基于下述两个理由,允许他们出售射杀海象权利的做法在道德上仍是可以加以反对的。
第一个理由认为,这个古怪的市场迎合了一种不正当的欲望,因此在对社会功利做任何一种计算的时候,这种欲望都不应当被重视。无论你是如何看待巨兽狩猎的,这都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巨兽猎杀。在没有任何挑战或刺激的情况下近距离射杀一头无力抵抗的动物的欲望,亦即为了完成一项纪录的那种欲望,是不值得去满足的,即使这样做可以为因纽特人提供额外的收入。第二个理由认为,因纽特人把分配给他们的射杀海象的权利出售给非因纽特人,首先是腐蚀了他们的国家赋予他们部落的特权的意义和目的。尊重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尊重他们长久以射杀海象为生的方式是一回事,而把这种特权转变成一种赚钱的射杀副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20世纪后半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著的《经济学》乃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近来我翻看了该书的一个早期版本(1958年版),想看一看他所认为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他用传统的研究对象把经济学界定为一个“由价格、工资、利率、股票和债券、储蓄和贷款、税收和支出所构成的世界”。经济学的任务是具体的,同时也是受限制的:解释如何能够避免经济萧条、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研究那些“告诉我们如何能够保持高生产力”以及“如何能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各项原则。 [59]
今天,经济学已经与它传统的研究对象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让我们来看一看曼昆在他极富影响力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就什么是‘经济学’这个问题而言,它毫无神秘之处可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一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彼此之间所发生的互动关系。”
根据这种解释,经济学所关注的不仅有物质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问题,而且也涉及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互动以及个人据以做出决定的各项原则。曼昆指出,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 [60]
关于激励措施的讨论在当代经济学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因此可以用它来界定该学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Steven D. Levitt)和斯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在《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的开头几页中写道:“激励措施乃是现代生活的基石”,因此“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对激励措施的研究”。 [61]
人们很容易忽视上面这个定义的新颖之处。激励措施这个说法乃是经济学思想在最近的一个发展。“激励”这个词语不曾出现在亚当·斯密或其他经典经济学家的论著中。 [62] 实际上,这个词语直到20世纪才开始进入经济学的表述,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记载,这个词语最早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出现,是在1943年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查尔斯·威尔逊先生……极力敦促战时的各个行业采取‘激励付酬方式’——这就是说,如果工人生产得越多,他们就能拿到越多的钱。”由于市场和市场思维方式的影响力不断强化,所以“激励措施”这个术语的使用在20世纪后半叶也突然盛行起来。根据Google网站的图书搜索,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该术语的使用率上升了400多个百分点。 [63]
把经济学看成是对各种激励措施的研究,无异于让市场侵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它也赋予了经济学家一种积极的角色。加里·贝克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那些被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影子价格”乃是不明确的价格,而不是实际的价格。它们是经济学家们想象、假设或推断出的类似隐喻的价格。相反,激励措施乃是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设定、规划和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各种干预措施。这些激励措施乃是促使人们减肥、更积极地工作或减少污染的各种方式。列维特和都伯纳写道,“经济学家们热爱激励措施。他们喜欢构想它们并将其付诸实施,研究它们并对其进行修正。典型的经济学家相信,这个世界还没有提出一个他无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只要他被给予一只自由的手去设计恰当的激励方案。他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总是那么漂亮——它可能包含强制或过度惩罚或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但令人放心的是,那个最初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一项激励措施可以是一枚子弹、一个杠杆、一把钥匙:常常是一个可以改变某种处境的有着惊人力量的、微小的举措”。 [64]
这与亚当·斯密把市场视作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形象相去甚远。激励措施一旦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石”,市场就会成为一只沉重的手,一只具有操控力的手。(让我们回想一下鼓励节育和鼓励学生取得好成绩的金钱激励措施)。列维特和都伯纳指出:“大多数激励措施不会自发出现,需要某个人——一位经济学家或一位政治家或一位家长——去发明它们。” [65]
激励措施在现代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而且还需要某人有意识地去发明它们;这个事实可以见之于最近流行起来的一个不怎么文雅的新动词:“激励”( incentivize)。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说法,激励就是“通过提供一种(通常是金钱方面的)激励措施来驱动或鼓励(一个人,特别是雇员或消费者)”。这个词可追溯至1968年,但却是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特别是在经济学家、公司总裁、行政官员、政策分析师、政治家、社论作者那里。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个词很少出现在著作中。自那以后,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了1 400个百分点。 [66] 在LexisNexis网站上,对一些主要报刊的搜索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
在主要报刊上“激励”和“激励措施”出现的次数: [67]
20世纪80年代 48
20世纪90年代 449
21世纪前10年 6159
2010~2011年 5885
近来,“激励”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了总统的演讲中。乔治·布什是第一位在公开演讲中使用该术语的美国总统,他一共使用了两次。克林顿在8年任期内只使用过一次,与小布什差不多。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头3年,就使用“激励”一词多达29次。他希望激励医生、医院和医疗卫生供应者更加关注预防性措施,并希望“鼓动、刺激和激励银行”为那些负责任的房主和小企业提供贷款。 [68]
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喜欢使用这个词。在对银行家和企业界领袖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呼吁他们更努力地去“激励”一种“敢于冒险的投资文化”。他在2011年伦敦骚乱后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的时候抱怨道,这个国家及其机构“此前一直在容忍、姑息,有时甚至在激励人性中某些最糟糕的方面”。 [69]
尽管经济学家们有了这种新的激励嗜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仍坚持要对经济学和伦理学(即市场逻辑和道德逻辑)进行区分。列维特和都伯纳解释说,经济学“绝不做道德买卖。道德所代表的是我们希望世界运作的方式,而经济学所代表的则是世界实际运作的方式”。 [70]
有人认为,经济学乃是一门独立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不过,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但是眼下经济学所持的那种傲慢的抱负,却使得上述主张很难得到辩护。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得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经济效率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呢?很可能是为了使社会功利(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偏好总和)最大化。正如曼昆所解释的那样,资源的有效配置会使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最大化。 [71] 那么,为什么要使社会功利最大化呢?很多经济学家不是忽视这个问题,就是求助于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
但是功利主义会招致一些类似的批评。与市场逻辑最为相关的批评会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应当在不考虑各种偏好的道德价值的情形下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偏好?如果一些人喜欢歌剧,而另一些人喜欢格斗或摔跤,我们是否就不该指手画脚,而且在计算功利的时候给予这些偏好以同等重要的地位? [72] 当市场逻辑关注物质商品(诸如汽车、烤炉和平板电视)的时候,上述那种批评是无关宏旨的;我们有理由假定,物品的价值就是一个消费者偏好的问题。但是当市场逻辑被运用到性、生育、孩子抚养、教育、健康、刑罚、移民政策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时,我们就不太有理由假定说,每个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这些充满道德意义的领域中,一些评价物品价值的方式可能会比另一些方式更重要,也更为恰当。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还应当在不追究其道德价值的情形下无倾向地满足这些偏好。(你想教小孩读书的欲望是否真的应当与你的邻居想近距离射杀海象的欲望具有同等价值?)
所以,当市场逻辑被扩展运用到物质商品以外的领域时,它必然要“进行道德买卖”,除非它想在不考虑它所满足的那些偏好的道德价值的情形下盲目地使社会功利最大化。
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认为,市场的扩张使得市场逻辑与道德逻辑(也就是解释世界与改善世界)之间的区分变得更为复杂了。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之一乃是价格效应:当价格上涨时,人们就会少买东西;而当价格下跌时,人们就会多买东西。在我们谈论诸如平板电视市场的时候,这项原则在一般意义上讲是可靠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把这项原则运用到那些受非市场规范调整的社会惯例——诸如按时去托儿所接孩子——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可靠了。当迟接孩子要支付的价格上涨的时候,迟接孩子的父母反而增加了。这个结果表明,规范的价格效应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把一种物品市场化会改变它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给迟接孩子的事情定价,改变了这里的规范。曾经按时接孩子被视作道德义务(不给老师带来不便)的那种东西,现在却被看成了一种市场关系,其间,迟接孩子的家长只需要向老师支付延时的服务费用就可以了。作为一种结果,激励措施在这里反而使迟接孩子的父母增加了。
托儿所的例子表明,当市场侵入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时,规范的价格效应便会失效。增加迟接孩子的(经济)成本,并没有减少迟接孩子的父母,反而增加了。所以,为了解释世界,经济学家就必须弄清楚,给某种活动定价是否会把非市场规范排挤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还必须对影响某种特定做法的各种道德认识进行调查研究,并确定(通过提供一种金钱的激励措施或一种非激励措施)把这种做法市场化是否会取代那些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可能会承认,为了解释世界,他/她必须研究道德心理学或道德人类学,也就是必须弄清楚相关领域所盛行的是什么规范以及市场会如何影响它们。但是,为什么这意味着要考虑道德哲学?基于以下理由:
在市场侵蚀非市场规范的地方,经济学家(或某个人)就必须确定这是否代表我们失去了我们应予以关注的某种东西。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家长是否不再为迟接孩子而感到内疚,并是否应当用一种更为工具性的方式来看待他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如果付钱鼓励孩子读书会使孩子把读书看成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并且会减少读书本身的乐趣,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呢?问题的答案会依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个问题使我们不只是对某种金钱激励措施是否会起作用这一点进行预测。它还要求我们对下述问题做出道德评价:金钱可能会侵蚀或将其排挤出去的态度和规范具有何种道德重要性?非市场规范和预期的缺失是否会以我们感到懊悔的方式改变那种活动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应当避免把金钱激励措施引入这种活动之中,即使这些措施有可能带来某种好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相关活动以及界定该活动的规范的性质和目的。即便是托儿所在这个方面也各有差异。在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中,父母们每个星期都会自愿花几个小时去做义工;而在一个传统的托儿所中,父母们则会付钱给老师让他们去照顾孩子,尔后去干自己的事情。因此,就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与一个传统的托儿所相比较而言,取代人们对彼此义务的共同预期会给前者带去更多的伤害。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处于道德领域之内。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依赖金钱激励措施,我们需要追问这些激励措施是否会腐蚀那些值得我们予以保护的态度和规范。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市场逻辑必须变成道德逻辑。不论如何,经济学家必须“进行道德买卖”。
是否有某些东西是不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哪些物品和活动是可以正当买卖的,而哪些物品和活动是不可以正当买卖的?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个略微不同的问题来着手探讨上述问题,而这个略微不同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某些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
就上述“是否有某些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这个问题而言,大多数人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可以以“友谊”为例。假设你想有更多的朋友,那么你会设法去买一些朋友吗?这是不可能的。稍稍一想,你就会意识到,就“友谊”而言,“购买”这种方式是无效的。一个雇来的朋友与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雇人来做你的朋友一般都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当你出门时帮你收信件,必要时帮你照看小孩,或者扮演情绪治疗专家的角色聆听你的苦恼并给你同情性的建议等。眼下,你甚至可以通过为你的Facebook网页雇用一些俊男美女“朋友”来增加你的网络知名度,而价钱是每位“朋友”每月99美分。当被使用的照片(大多数是模特的照片)未得到授权时,虚拟朋友网站则会被停止运营。 [1] 尽管所有这些服务都可以拿来买卖,但实际上你是不可能买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总之,用来买友谊的金钱要么把友谊消解掉,要么使友谊完全变味。
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诺贝尔奖的情形。假设你拼命想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你按正常的方式却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时,你可能会突然产生去买一项诺贝尔奖的念头。但是,你很快会意识到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因为诺贝尔奖不是金钱能够买的那种东西。美国棒球大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最有价值球员奖也不是金钱能够买的那种东西。如果某位前“诺贝尔奖”得主或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得主愿意卖掉他的奖品,那么你就可以买到这个奖品,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奖品陈列在你的客厅里。但是,你却无法买到那个奖项本身。
这不只是因为“诺贝尔委员会”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不出售这些奖项。即使“诺贝尔委员会”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拍卖他们的奖项,比如,一年出售一个诺贝尔奖,那么所购得的那个奖也定会与真正的奖不一样。市场交易会消解掉赋予该奖项以价值的那种善(good)。这是因为诺贝尔奖是一种表达尊敬的物品。购买诺贝尔奖就是在消解你追求的那种物品。一旦人们得知有人购买了诺贝尔奖,那么诺贝尔奖也就不再会传递出或表达出人们被授予该奖时所得到的那种尊敬和承认。
美国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的情况亦是如此。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也是表达尊敬的物品;如果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是买来的,而不是靠赛季的本垒打比赛获胜或其他精彩表现获得的,那么这个最有价值球员奖的价值就会被消解掉。当然,表征一个奖项的奖品与这个奖项本身之间是有区别的。事实的确如此,美国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得主卖掉了他们的奥斯卡金像,或把这些奥斯卡金像留给了他们的继承人,而他们的继承人则把金像卖掉了。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 house)和其他拍卖行拍卖了其中的一些奥斯卡金像。1999年,迈克尔·杰克逊用154万美元购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奥斯卡金像。颁发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反对买卖奥斯卡金像,因此它现在要求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签署一项承诺不出售奥斯卡金像的协议。颁发奥斯卡奖的官方机构不想将符号性的雕像变成商业性的收藏品。不论收藏家是否有能力购买奥斯卡金像,购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与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显然是不一样的。 [2]
上述这些较为显见的事例为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提供了某种启示,而那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东西是金钱能够买到但却不应当买的?让我们来考察一种能够买但它的买卖却会在道德上引起争议的物品,比如,人的肾脏。一些人为器官移植市场辩护,而另一些人则发现这种市场存在道德争议。如果购买肾脏是错误的,那么其问题并不会像诺贝尔奖那样:金钱会消解该物品的价值。假设肾脏移植很匹配,那么肾脏就会发挥功用,而与支付金钱无关。因此,为了确定肾脏是否应当拿来买卖,我们必须做一番道德探究。我们必须检视赞同或反对器官买卖行为的各方观点,并确定哪方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婴儿买卖的事例。几年前,“法律和经济”运动(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曾建议用市场手段来分配那些供收养的婴儿。波斯纳承认,一些更讨人喜欢的婴儿相较于不太讨人喜欢的婴儿会要求收养人出更高的价格。但是他论辩说,在分配供收养的婴儿这件事情上,自由市场会比现行的收养制度做得更好,因为现行的收养制度虽说允许收养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却不允许拍卖婴儿或索要市场价格。 [3]
许多人都不赞同波斯纳的这项建议。他们主张,不论市场多么有效,孩子都不应当拿来买卖。在认真审视这场争论以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像肾脏市场一样,婴儿市场也不会消解掉婴儿购买者试图获得的那种物品。在这个方面,买来的婴儿不同于雇来的朋友或买来的诺贝尔奖。如果存在一个收养婴儿的市场,那么人们以现价购买之后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孩子。这样一个市场是否存在道德争议,乃是一个需要我们更进一步予以思考的问题。
因此,乍看起来,下述两类物品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区别:一类东西(如朋友和诺贝尔奖)是金钱不能买的,而另一类东西(如人的肾脏和孩子)是金钱能够买的,但在是否应当买卖上存有争议。然而,我建议,这二者的区别并没有乍看上去时那么清晰明确。如果我们审视得更仔细些,那么我们便可以洞见上述显见的情形(即购买朋友和诺贝尔奖)与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即购买人的肾脏和孩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上述显见的情形中,金钱交易损毁了人们所购买的物品,而在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中,物品会在买卖后得以存续,但结果却有可能遭到贬损、腐蚀或减少。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一些介于购买友谊与购买肾脏之间的事例来探究上述两种情形中的那种联系。如果金钱不能购买友谊,那么友谊的表征或亲密的、爱慕的或懊悔的表示又如何呢,也不能买吗?
2001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关于一家中国公司的报道。该公司提供一项独特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向某人(如已经分手的恋人或已经闹翻的商业合作伙伴)道歉,而你又不想亲自去向他道歉,那么你便可以雇用天津道歉公司代表你去道歉。天津道歉公司的口号是“我们替你道歉!”这篇文章还说,专业道歉工作人员是“一些拥有大学学历、身穿深色制服的中年男性和女性。他们是拥有‘出色口头表达能力’和重要生活经验的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当然,他们在咨询方面还接受过额外的培训”。 [4]
我不知道天津道歉公司是否取得了成功,甚或也不知道该公司是否依然存在。但是,我在读到这篇有关天津道歉公司的报道时产生了一种疑惑:买来的道歉可行吗?如果某人冤枉了你或冒犯了你,然后再派一个雇来的道歉者向你赔罪,你会感到满意吗?它也许取决于各种情境,甚或也可能取决于成本。你会认为一个昂贵的道歉比一个廉价的道歉更有意义吗?或者说,需要道歉之人的道歉行为应该包含懊悔之意,以至于它是不能被外包的?如果雇人道歉无论花费如何巨大都无法达到本人道歉的效果,那么道歉就像朋友一样也是金钱不能买的那类东西。
让我们考虑一下另一种与友谊密切相关的社会惯例,即对新人致婚礼祝词。按照传统习俗,婚礼祝词是由男傧相(通常是新郎最亲密的朋友)向新婚夫妇表达温暖、诙谐和衷心的美好祝愿。但是,构思一篇优雅的婚礼祝词并不简单,而且许多男傧相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于是,一些男傧相会去网上购买婚礼祝词。 [5]
“完美祝词网站”(ThePerfectToast.com)就是专门为人代写婚礼祝词的一家主要的网站。“完美祝词网站”自1997年开始运营。你只要在网上回答一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新娘和新郎是如何相遇的、你会如何描述新娘和新郎,以及你是想要一篇幽默风趣的祝词还是一篇感情真挚的祝词等),你便可以在3个工作日内收到一篇量身定制的3~5分钟的祝词。代写一篇婚礼祝词的价格是149美元,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对于那些支付不起代写婚礼祝词价格的男傧相来说,其他一些网站——如“即时婚礼祝词网站”(InstantWeddingToasts.com)——为他们出售规范的、事先写好的婚礼祝词,每篇价格为19.95美元,而如果客户对服务不满意,则可以保证退款。 [6]
假设在你的婚礼上,你的伴郎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并让你热泪盈眶的婚礼祝词。事后,你了解到你的伴郎给你们的婚礼祝词并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而是从网上买来的。对此,你会在意吗?这篇婚礼祝词在当下的意义会不及你的伴郎当初念它的时候(即在你不知道这篇婚礼祝词是由枪手代写的时候)的意义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回答说,“不及”,也就是说,买来的婚礼祝词不如由伴郎亲自撰写的婚礼祝词更有价值。
有人可能会论辩说,各国的总统和首相通常也会雇用演说稿撰写者,却没有人会为此指责他们。但是,婚礼祝词并不是国情咨文,而是对友谊的一种表达。尽管买来的婚礼祝词在达到预期效果的意义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效果的达到却可能要取决于一种欺骗因素。这里有一个测试:如果你为了在最好朋友的婚礼上发表婚礼祝词这件事感到头疼,而去网上买了一篇感人且真挚的婚礼祝词杰作,那么你是会曝光购买婚礼祝词这个事实,还是会竭力掩盖这个事实?如果买来的婚礼祝词需要借助掩盖它的出处来达到效果,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买来的婚礼祝词乃是对祝福人亲自撰写的婚礼祝词的一种腐蚀。
从某种意义上讲,道歉和婚礼祝词是金钱能够买的物品。但是,买卖道歉和婚礼祝词却改变了它们的品质,并且贬低了它们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友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送礼。与婚礼祝词不同,礼物难免有物质的一面。但是,就一些礼物而言,其在金钱方面不那么显眼;而就另一些礼物而言,其在金钱方面则相对明显。在最近几十年里,礼品货币化已经成了一种趋势,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日趋商品化的另一个例子。
经济学家不喜欢送礼。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学家很难把送礼视作一种理性的社会惯例。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相比送礼直接给现金来得更好。如果你设想人们一般都了解自己的偏好,而且送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高兴,那么给钱就是最好的方式。即使你品味高雅,你的朋友也可能不喜欢你挑选的领带或项链。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要最大化你的礼物给人的好处,那么你就不要买礼物,只要把你本来买礼物所要花费的钱给他就可以了。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或者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你原本打算买的物品,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某种会给他带去更大愉悦的物品。
这就是经济学家反对送礼的逻辑。这种逻辑受制于一些限定条件。如果你碰巧看到你朋友会喜欢但却不甚熟悉的物品(比如,一种最新的高科技小物件),那么这个礼物就会比你信息闭塞的朋友用同样的钱所购买的东西给他带去更大的快乐。但是,这是一个与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相符合的特殊情形,而经济学家的这个基本假设认为,送礼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受赠人的福利或功利最大化。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乔尔·沃德佛格(Joel Waldfogel),一直把送礼的经济低效这个问题作为他长期研究的课题。所谓“低效”,沃德佛格意指两种价值间的落差:一个是你婶婶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价值120美元的带有菱形图案的毛衣)对你的价值(可能非常小),另一个是(如果你婶婶把购买该毛衣的120美元现金给你)你会买的那个东西(比如,iPod)对你的价值。1993年,沃德佛格在其论文《圣诞节无谓损失》(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中,已然注意到了与节假日送礼相关的挥霍行为的盛行。沃德佛格在其近著《吝啬经济学:节假日不该送礼的理由》(Scroogenomics: Why You Shouldn’t Buy Presents for the Holidays)中修订并详尽阐述了前述论题:“总而言之,当其他人为我们买东西(如衣服、音乐制品或其他任何东西)时,他们所挑选的东西很可能不是我们会为自己所挑选的东西。不论他们如何用心良苦,我们都能料到他们的选择是无法令我们满意的。相较于他们的支出本应带给我们的满意度而言,他们的选择可以说侵损了他们所付金钱的价值。” [7]
按照规范的市场逻辑,沃德佛格得出结论,在大多数情形中,还是直接给钱来得更好:“经济学理论和常识都使我们做出这样一种预期:就每一欧元、每一美元或每一谢克尔的花费而言,我们为自己买东西要比我们为他人买礼物会使我们更满意……买礼物一般都会侵损物品的价值,而且只有在极少数的最好特例中,买礼物才能令人觉得与给现金一样好。” [8]
在阐明了反对送礼的经济学逻辑之后,沃德佛格又对这种低效的做法侵损了多少价值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让礼物受赠人对他们所收到的礼物进行估价,并询问他们愿意为他们所收到的礼物付多少钱。他的研究得出结论:“就每一美元的花费而言,我们认为,我们所收到的礼品相较于我们为自己所买的物品在价值上要少20%。”就是这个20%使得沃德佛格能够估算出美国全国范围内在节假日送礼所将产生的总“价值损失”:“假定每年美国节假日人们送礼要花费650亿美元,这意味着,与我们以通常的方式(即精打细算的方式)为我们自己花费650亿美元所获得的满意度相比较,我们会因为送礼而将少获得130亿美元的满意度。美国人是在以一种‘大肆侵损物品价值’的方式庆祝节假日。” [9]
如果送礼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低效活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在规范的经济学假设范围内很难得到回答。然而,格雷戈里·曼昆在他所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却勇敢地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曼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送礼是一个奇怪的习俗”,但他同时也承认,如果在你男朋友或女朋友过生日时给他/她现金,而不是一件生日礼物,那一般来说是一个馊主意。这是为什么呢?
曼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送礼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模式——这是一个意指用市场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术语。比如,一家拥有高质量产品的公司花费巨额费用来做广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直接游说顾客购买其产品,而且也是在向他们“发送信号”:负担代价高昂的广告意味着该公司对其产品质量有足够的自信。而曼昆的言下之意是,送礼也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发送信号。一个为送给女朋友礼物而精心琢磨的男人“心里有一则私密信息,即他的女朋友想知道:他是否真的爱她?为她挑选一件好的礼物是他爱女朋友的一个信号”。既然挑选礼物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么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乃是他“传递他爱女朋友这一私密信息”的一种方式。 [10]
曼昆对上述问题的解释,是一种思考恋人与礼物问题的极其呆板的方式。“发出”爱的“信号”,与表示爱是不一样的。说发送信号,实际上是在错误地假定,爱是一则由一方传递给另一方的私密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给现金也会行之有效——钱给得越多,信号就越强,进而爱意(想必)也就越浓。但是,爱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一个私密信息的问题。爱是一个人与另一人相处并回应另一人的行为或感情的一种方式。礼物(尤其是花心思的礼物)可以是爱的一种表示。从表示的角度来看,好的礼物不仅要让人高兴(即满足受赠人消费偏好意义上的那种高兴),而且还反映了赠送者与受赠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送礼要花费心思的原因所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礼物都可能有上面那种“表示”的意味。如果你出席一个远房兄弟的婚礼或某个商业伙伴的小孩的成人礼,那么较好的做法很可能是从婚姻登记处买一件礼物或者直接给现金。但是,给朋友、恋人或配偶现金而不是某件精心挑选的礼物,所传递的就是不把他/她放在心上的某种冷漠。这就好像用金钱代替了对朋友、恋人或配偶的关爱似的。
经济学家知道礼物有表示的一面,尽管他们的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这一点。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是一位经济学家和一名博主;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最好的礼物是现金,但是不作为经济学家的我则反对这种观点。”功利主义观点认为,理想的礼物是我们会为自己购买的那种物品:假设某人给了你100美元,而你用这100美元为你自己的车买了一副轮胎。这就是使你的功利最大化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塔巴罗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如果你的恋人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副你的汽车的轮胎,那么你可能不会感到特别高兴。塔巴罗克指出,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宁愿送礼的人送给我们某种奇特的东西,也就是某种我们不会为自己购买的东西。至少,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知己那里收到可以表达“狂野的自我、激情的自我或浪漫的自我”的礼物。 [11]
我认为,塔巴罗克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送礼物之所以并不总是对有效功利最大化(efficient utility maximizing)的非理性背离,乃是因为礼物并不只是事关功利的问题。一些礼物是对某些确定、质疑或重释我们的身份关系的一种表达。这是因为友谊除了对友谊双方彼此有用以外,还有更多的意义。它的意义还包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有助于人的性格的成长和人对自我的认知。正如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的那样,友谊在最佳状态的时候还具有塑造和教育的意义。然而,将朋友之间所有形式的送礼都货币化,会在用功利性规范支配一切的过程中把友谊腐蚀掉。
甚至用功利主义观点来审视送礼这一行为的经济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到,送钱乃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尤其在地位同等者之间、配偶之间以及其他重要的人之间更是如此。在沃德佛格看来,这便是他所谴责的那种低效的渊源。那么,依照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在激励人们坚持这样一种大规模侵损价值的习惯呢?他认为,激励人们送礼而不给钱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金被认为是一种承载某种恶名的“庸俗之礼”。不过,他并没有追问人们把送钱视为庸俗的观点是对还是错。相反,他撇开这种恶名所具有的减损功利的不良倾向,反而把这种恶名视为一种没有任何规范意义的非理性的社会事实。 [12]
沃德佛格认为:“如此多的圣诞礼物是实物而非现金,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认为送钱太俗。如果送钱没有这种恶名,那么送礼的人就会给现金,受赠人也会用这笔钱去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这也会使受赠人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13] 斯蒂芬·都伯纳和史蒂文·列维特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即人们在送礼时之所以不愿意送现金,多半是一种“社会禁忌”(a social taboo)所致,而这种禁忌“粉碎了经济学家关于完美、有效交易的梦想”。 [14]
对送礼的经济学分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说明了市场逻辑所具有的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这种分析表明了市场逻辑是如何偷偷地预设了某些道德判断的,尽管它声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沃德佛格并没有评论过人们讨厌送钱的正当性,而且也从来没有追问过它是否有可能得到正当性证明。他只是假定,它是实现功利的一种非理性障碍,即一种在理想状态下应当加以克服的“功能失调的惯例”。 [15] 他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送钱的恶名会反映一些值得珍视的规范,比如那些与友谊密切相关的关爱规范。
坚持认为所有礼物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功利最大化,也就是未经论证地假定:首先,功利最大化的友谊观是一种最合乎道德的观念;其次,对待朋友的正确方式就是满足朋友的偏好,而非质疑、扭曲或减损他们的偏好。
因此,反对送钱的经济学理据并不是道德中立的。它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友谊观,亦即一种被许多人都认为不值一提的友谊观。然而,不论对送礼的经济学分析进路在道德上存在何种不足,这种分析进路却正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而这使得我们必须去直面送礼这个例子所具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尽管它的道德假定存有争议,但是思考送礼的经济学方法却正在逐渐成为一种事实。在过去20年里,送礼的金钱面相已渐渐浮出水面。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礼品卡(gift card)兴起的情形。节假日的购物者正越来越趋向于赠送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礼品券或礼品卡(这些礼品券或礼品卡可以在零售店中兑换商品),而不是自己去寻找并购买恰当的礼物。礼品卡代表了一种折中的送礼形式,居于挑选具体礼物与给现金这两种送礼形式之间的形式。礼品卡不仅使得送礼人的送礼活动变得更简单,而且也给受赠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一张塔吉特、沃尔玛或萨克斯第五大道的50美元礼品卡,通过让受赠人选择他/她真正想要的某种东西的方式而避免了一件毛衣因为小两码而导致的那种“价值损失”。然而,礼品卡无论如何都是有别于给现金的。的确,受赠人确切地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因为,礼品卡的货币价值是明确的。尽管这是事实,但是特定商场的一张礼品卡相对于给现金而言要少很多恶名。或许,选择一家合适的商场所传递出的那种贴心的因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那种恶名。
节假日礼物的货币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当时,越来越多的送礼人开始给亲友送礼品券。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礼品券向“礼品卡”的转变,加速了节假日礼物货币化的趋势。从1998年到2010年,礼品卡年销售额几乎增加了8倍,超过了900亿美元。根据消费者问卷调查,礼品卡是人们现在所需求的最流行的节假日礼物,居于服装、视频游戏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珠宝和其他物品之前。 [16]
传统主义者对这种趋势深表哀叹。朱迪丝·马丁(Judith Martin)是以“礼仪小姐”(Miss Manners)著称的礼仪专栏的作家;她抱怨说,礼品卡业已“掏空了节假日的心脏和灵魂。你的基本做法就是给人送钱,就是送钱让他们离开”。个人理财专栏作家莉兹·普利亚姆·韦斯顿(Liz Pulliam Weston)所担忧的是,“送礼这门艺术正在迅速蜕变成一种完全商业化的交易”。她问道:“从放弃现在的‘送礼’方式,到我们开始相互直接扔掷一叠一叠的美钞,难道还需要很长时间吗?” [17]
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向礼品卡的转变乃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直接给美钞会更好。理由是什么呢?尽管礼品卡减少了礼物的“净损失”,但是它们却无法把这种“损失”完全消除掉。假设你的叔叔给了你一张100美元的、可以在“家得宝”超市购买物品的礼品卡。这要比给你一个你不想要的价值100美元的工具包好得多。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家装饰品,那么你还是宁愿要现金的。毕竟,金钱就像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物品的礼品卡一样。
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市场已经有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些网店现在(以低于礼品卡面值的价格)用现金购买礼品卡,然后再倒手转变这些礼品卡。例如,一家名叫“卡片超市”(Plastic Jungle)的网店会用80美元的价格收购你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家得宝礼品卡,然后再以93美元的价格转售该礼品卡。礼品卡的折扣率会根据礼品卡所能使用的商场的受欢迎度而变化。一张面值100美元的沃尔玛或塔吉特礼品卡,“卡片超市”网店会用91美元的价格收购。然而,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巴诺书店礼品卡,如果出售给“卡片超市”网店,很遗憾只能卖到77美元,略少于一张面值100美元的汉堡王礼品卡所能卖到的79美元。 [18]
对于那些关注礼物净损失的经济学家来说,上述二手市场可以量化出你通过送礼品卡而非给现金这种方式强加给受赠人的经济损失:礼品卡的折扣率越高,礼品卡的价值与现金价值之间的落差也就越大。当然,不论是送礼品卡,还是给现金,都无法体现传统送礼方式所表达的那种贴心和关爱。贴心和关爱这些美德在礼物转变为礼品卡(并最终转变为现金)的过程中被削弱了。
一位研究礼品卡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调和“现金的经济效率”与“贴心的传统美德”二者的方法:“一个打算送礼品卡的人需要记住给现金的可能好处,并附上一张给受赠人的便条,告诉他这笔钱可以在__(此处填写商场的名称)消费;也就是在送礼品卡时再加上一点有益的体贴。” [19]
送钱并附带一张令人高兴的便条(建议受赠人在哪里花掉这些钱),乃是一种被彻底解构的礼物。这就好比将功利元素和表示规范分别打包在两个盒子里,再用一根带子把它们系在一起。
我最喜欢的一个送礼商品化的例子是一种提供电子化的礼物转送(electronic regifting)系统,该系统最近获得了专利。《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描述:假设你婶婶送给你一个水果蛋糕作为圣诞礼物。水果蛋糕公司在发给你的电子邮件中通知你将得到这样一份贴心的礼物,同时给你提供下述3项选择:接受交付、用它交换某种其他东西或将这个水果蛋糕送给你礼物名单上某位不会拒绝的人。由于交易是在网络上发生的,所以你不必麻烦地将水果蛋糕重新打包,再把它送去邮局。如果你选择转送礼物,那么新的受赠人也会得到上述3项同样的选择。因此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没有人需要的水果蛋糕可以经由网络空间而无限制地转赠下去。 [20]
一种可能令人感到糟糕的情况是:由于零售商执行一种透明的政策,所以水果蛋糕上述“旅程”中的每一位受赠人都能够知晓这个水果蛋糕的行程表。这会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知道这个水果蛋糕已遭到了前面好几位受赠人的拒绝,而且直到现在才勉强地硬塞给你,那么这很可能会削减你因得到这份礼物本应产生的感激之情,进而消解掉该礼物的情感价值。这有点像这种情况:你发现你最好的朋友事先在网上购买了一份感情真挚的婚礼祝词。
尽管金钱买不来友谊,但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却能买到友谊的表征和表达方式。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把道歉、婚礼祝词和礼物转换成商品并不会把它们完全毁掉。但是,它确实侵损了它们。它们之所以遭到侵损乃与下述原因有关,即金钱不能用来买朋友:友谊以及维系友谊的社会惯例乃是由某些规范、态度和美德构成的。把这些惯例商品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要置换这些规范(如同情、宽容、贴心和关爱),并用市场价值观来替换这些规范。
雇来的朋友与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说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乃是金·凯瑞(Jim Carrey)在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所扮演的角色。金·凯瑞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看似平安幸福的城镇里,而该角色不知道的是,这个城镇实际上是一档现实电视秀节目的摄影棚。金·凯瑞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楚,他的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也都是雇来的演员。但是,这当然不是金·凯瑞雇来的,而是电视制片人雇来的。
友谊的关键在于:我们(通常)无法买到朋友的原因(即买卖朋友会损害这种关系),阐明了市场是如何腐蚀这种友谊表达方式的。尽管买来的道歉或婚礼祝词让人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但是它们却已然受到了玷污和贬低。尽管金钱能够购买道歉和婚礼祝词,但是它们只是真正的道歉和婚礼祝词的低级形式。
荣誉物品也很容易遭到相似的腐蚀。金钱不能用来买诺贝尔奖,但是其他形式的荣誉和认可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名誉学位的情况。大学和学院会把名誉学位授予杰出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公职人员。但是,有一些名誉学位的得主却是事先把大笔钱捐给授予其名誉学位的机构的慈善家。就此而言,这类学位究竟是买来的,还是真正的荣誉?
名誉学位可以是含糊的。如果大学或学院直言不讳地陈述授予名誉学位的理由,那么这种直言不讳就会消解掉它的美好。假设学位授予仪式上所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样写道:“我们基于杰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成就而授予他们名誉学位。但是,我们授予你这个学位,是为了感谢你捐赠给我们1 0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这样的奖励很难被视作一种名誉学位。当然,名誉学位上的赞美之词永远不会那样写。它们会论及公共服务、捐赠善举,以及对大学使命的奉献,亦即一些会模糊名誉学位与买来的学位这二者之间区别的赞美之词。
我们也可以就入读著名大学的名额是否可以买卖的问题提出类似的问题。大学不会拍卖它们的入学名额,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拍卖它们的入学名额。如果许多有严格遴选程序的大学和学院都将一些新生名额卖给最高出价者,那么它们就可以增加学校的财政收入。但是,即使它们想使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大化,它们也不会把所有新生名额都拿来拍卖。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教学质量,而且也会削弱考生考进大学的荣誉,进而还会减少需求。如果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买到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名额,而且这种情况广为人知,那么你被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或者你的孩子被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也就没有什么可引以为傲的了。它顶多是那种类似于“我买得起一艘游艇”般的骄傲。
然而,假设绝大多数的入学名额都是按照成绩来分配的,只有少数入学名额是悄悄拿来出售的。同时,让我们再假设,大学和学院在决定是否录取你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高中成绩;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成绩;课外活动;种族、民族及地域等因素;运动技能;校友子女优先因素等),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说哪些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在上述两种条件下,大学和学院可以把一些入学名额卖给富有的捐赠人,而同时又不减损学生在被顶级大学录取时所能感受到的那份荣誉。
高等教育的评论家认为,上述情况大抵就是今天许多大学和学院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把“校友子女优先”(即优先考虑录取校友的孩子)说成是一种呵护富人的做法。而且他们还指出了这样一些情形:一些大学和学院为一些不怎么优秀的申请者放宽了录取标准,因为这些申请者的父母非常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巨款,尽管他们并不是校友。 [21] 然而,捍卫这种做法的人则论辩说,私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校友和富有捐赠者的捐赠,而且这些捐赠也可以使大学为那些不怎么富裕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财政援助。 [22]
因此,与诺贝尔奖不同,大学和学院的入学名额是一种可以拿来买卖的物品,只要学校不公开兜售它们。大学和学院是否应当这样做,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买卖大学和学院入学名额的想法会面临两种反对意见。一种是关于公平的,另一种是关于腐败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认为,为了让富有捐赠者为学校基金进行巨额捐赠而录取他们孩子的做法,对于那些出生在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的申请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反对意见把大学教育视作赢得机会和改变社会地位的一种渊源,并担心为富家子弟提供这种优惠条件的做法会固化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状况。
那种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制度诚信的问题。这种反对意见指出,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学生胜任有偿工作,而且还体现了一些理想:追求真理、弘扬学术和科学的卓越性、增进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尽管所有的大学都需要用钱来追求其目标,但是让筹集资金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会产生扭曲大学各种理想的风险,也会产生腐蚀赋予大学以存在理由的各种规范的风险。总之,这种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诚信,亦即一种制度对其基于理想的忠诚;而这一点正是众所周知的对“出卖”的指责所揭示的。
上述两种观点贯穿于“金钱应当和不应当买什么”的争论之中。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市场选择有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而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则是市场关系有可能侵损或消解的规范和态度。 [23]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肾脏的情况。的确,金钱能够购买他人的一个肾脏而同时不会损毁其价值。但是,人的肾脏应当拿来买卖吗?那些认为人的肾脏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人,一般都会基于下述两种理由中的其中一种来反对这种做法。第一,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对贫困者构成掠夺,因为他们选择出售他们的肾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公平理由)。第二,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促使人们把人贬低为、客体化为移植器官的一种集合体(腐蚀理由)。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孩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收养婴儿的市场。但是,我们应当这样做吗?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给出了两种反对理由。一种反对理由认为,把孩子拿来出售的做法会把不那么富裕的父母赶出这个市场,或者说,这样做会给不那么富裕的父母剩下一些最便宜的、人们最不想要的孩子(公平理由)。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给孩子标价会腐蚀“无条件的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不同孩子之间不可避免的价格差异还会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孩子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种族、性别、智力前景、身体素质或身体残疾,以及其他特征(腐蚀理由)。
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阐明上述两种认为市场具有道德局限的理由。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指向的乃是当人们在不平等或极需金钱的条件下买卖东西时会产生的那种不公正。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市场交换并不总是如市场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愿的。一个农民为了供养他正在挨饿的家人有可能会同意出售他的一个肾脏或一只眼角膜,但是他的同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实际上,这个农民有可能是迫于其恶劣的经济状况。
反对腐蚀的意见与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场估价或市场交换有可能会对某些物品和做法产生的贬损效应。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来买卖,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销蚀或腐蚀。反对腐蚀的意见不可能通过建立公平的交易条件而被消解,因为无论条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适用。
人们就卖淫问题所展开的长时间的争论,就表明了上述两种理由之间的区别。一些人反对卖淫,因为卖淫者很少有人是真正自愿的(如果有真正自愿的话)。他们论辩说,那些卖淫的人一般都是被迫的,不论是迫于贫穷、毒瘾,还是迫于暴力威胁。这种反对意见就是前述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但是,另一些人反对卖淫,则是因为不论妇女是否被迫卖淫,卖淫都会贬损妇女的人格。根据这种理由,卖淫是一种腐败/腐蚀,它会贬低妇女的人格,并致使人们用不健康的态度看待性问题。反对贬损妇女人格的意见,并不取决于卖淫者是否真正同意这样做;甚至在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中,甚至在高级妓女(她们喜欢这份工作并自由选择了这个职业)的情形中,这种反对意见也会谴责卖淫行为。
上述两种反对意见利用了不同的道德理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追求的是同意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平的背景条件下得以实现的那种同意理想。赞同用市场来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据之一就是市场尊重选择自由。市场允许人们自己选择是否按照某种给定的价格出售某种物品。
然而,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指出,一些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自愿。如果一些人极度贫穷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公平的讨价还价,那么市场选择就不是自由选择。因此,为了弄清楚某项市场选择是否是一种自由选择,我们就必须追问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哪些不平等现象会破坏有意义的同意。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平等在什么意义上会对不利一方构成强制,并会破坏他们所达成交易的公平性?
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利用的是一套不同的道德理想。它所诉诸的不是同意,而是相关物品(即那些被认为因市场估价和市场交易会受到贬损的物品)的道德重要性。因此,为了决定大学入学名额是否应当拿来买卖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大学应追求的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展开讨论,并对出售大学入学名额是否会损毁那些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问题进行追问。为了决定是否应当建立一个用于解决婴儿收养问题的市场,我们就必须追问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对买卖孩子是否会破坏那些规范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
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对市场的理解上存在不同:前者并不会因为某些物品是珍贵的、神圣的或无价的而反对把它们市场化;它反对在那种严重到足以产生不公平议价条件的不平等情形中买卖物品。它并不为人们反对在一个具有公平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将一些物品(不论是性、人的肾脏,还是大学入学名额)商品化的做法提供任何理据。
与之不同的是,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物品本身的性质以及应当用来调整这些物品的规范。因此,仅仅通过确立公平的讨价还价条件,并不能消除这种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个不存在能力和财富不公正差异的社会中,仍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应当购买的。这是因为市场不只是一种机制,而且还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因而,有时候,市场价值观会把一些值得我们关切的非市场规范排挤出去。
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市场价值观又是如何腐蚀、消解或取代非市场规范的呢?规范的经济学逻辑假定,将某一物品商品化(即将该物品标价出售)并不会改变该物品的性质,而且市场交易还可以在不改变物品本身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般都支持用金钱激励措施来激发所期望的行为;赞同倒卖珍贵的音乐会、体育赛事甚至教皇弥撒的门票;赞同用可交易的配额来分配有关排放、难民和生育的问题;赞同送现金而非其他礼物;赞同用市场来缩小各种物品(甚至是人的肾脏)供需之间的落差。如果你假定市场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态度不会减损交易物品的价值,那么市场交易就可以在使任何其他人都不受损的情况下使交易双方获益。
然而,上述假定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在上文业已考察了大量质疑该假定的事例。当市场侵入传统上受非市场规范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时,那种认为市场不会侵损或贬损其交易物品的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确认了常识所表明的这样一个道理,即金钱激励措施和其他市场机制会通过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方式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有时候,为某种特定行为支付酬劳,并不会使人们更多地这样行事,反而会使他们较少地这样行事。
多年来,瑞士一直都在设法寻找一个贮存放射性核废料的地方。尽管瑞士严重依赖核能,但是很少有社区想让核废料存放在它们那里。当时,被指定可能堆放核废料的一个地方是位于瑞士中部叫作沃尔芬西斯(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也就是在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公投前不久,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小山村的居民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居民是否会投票赞同在他们的社区里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如果瑞士国会决定在他们村建立核废料贮存点的话。尽管在该山村贮存核废料对居住在该地的街坊邻里来说被广泛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该山村居民的微弱多数(即51%的村民)却表示,他们会接受这一决定。显而易见,这些居民的公民义务感压倒了他们对风险的关切。后来,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增加了一个补偿观点,即假设瑞士国会提议在你所在的社区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并每年对该社区的每位居民进行现金补偿。那么,你会支持这种做法吗? [24]
调查结果表明:小山村居民的支持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经济激励的增加,减少了一半的支持率,即从原来的51%降到了25%。给钱的想法,实际上降低了人们赞同把核废料贮存在自己社区的意愿。此外,增加一项补偿额度的做法也不起什么作用。当经济学家后来增加了补偿额度的时候,结果也于事无补。甚至当所提供的年度金额高达每人8 700美元(远远超过瑞士一般人的月收入)时,该山村居民的支持率还是很低。人们对金钱补偿的类似反应(虽不那么明显),也可以见之于其他抵制放射性废料贮存点的社区。 [25]
于是我们要问,瑞士这个小山村的居民怎么啦?为什么更多的居民愿意无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而不愿有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呢?
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指出,给人们金钱让他们接受一项负担的做法会提高而非降低他们接受该项负担的意愿。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S·弗赖(Bruno S. Frey)和美国经济学家菲力克斯·奥伯霍尔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指出,价格效应有时候会受到道德考量(其中包括对共同善的承诺)的压制。对于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意愿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精神,亦即这样一种认识:整个国家都仰赖核能,因此核废料总得有个地方来存放。如果他们的社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核废料存放点,那么他们愿意承担这项负担。在这种公民承诺的背景下,给这个小山村居民以现金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贿赂,即设法贿买他们的选票似的。事实上,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通过宣称他们不可被贿赂这样一种方式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 [26]
你可能会认为,增加一项金钱激励措施只会强化原已存在的那种公共精神,进而增加人们对“设立核废料贮存点”这一举措的支持。两项激励措施(一种是金钱激励措施,另一种是公民精神激励措施)难道不比一种激励措施更强有力吗?然而,答案却未必。假定激励措施是一种加法因子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对于瑞士的良好公民来说,个人金钱补偿这种做法乃是把一个公民问题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市场规范的侵入把他们的公民义务感排挤了出去。
主持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在公共精神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如果用价格激励措施来让人们支持建设一个对社会有益处但在地方上却不受欢迎的核废料设施,那么它付出的代价要比规范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代价高得多,因为这类激励措施会把公民的义务感排挤出去。” [27]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当直接把设立核废料贮存点的决定强加给地方社区。高压政策要比金钱激励措施对公共精神更具有腐蚀性。让当地居民评估在其社区设立核废料贮存点对他们将会产生的各种风险;允许公民参与决定把核废料贮存点设于何处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个问题;赋予核废料贮存点所在社区权利,使它们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关闭危险的核废料贮存设施;以上这些方式肯定是一些要比简单地购买更能够得到公众支持的方式。 [28]
尽管现金补偿一般会令人反感,但是实物补偿却常常会受到欢迎。社区常常会接受政府因把一些不受欢迎的公共工程(如飞机场、垃圾填埋场和废品回收站)建在他们社区旁边而给予它们的补偿。然而,各项研究发现,如果这种补偿采取公共物品的形式,而不是现金的形式,那么人们更有可能接受这种补偿。相较于金钱补偿,人们更乐意接受这样一些补偿形式,比如,为他们的社区修建公园、图书馆、学校、社区中心、慢跑小道和自行车车道等。 [29]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这种情况有点令人费解,甚至是非理性的。按照一般推论,现金总是要优于实物性的公共物品,其原因正如我们在讨论送礼时所揭示的。金钱是能够用来交换物品的通货,是普遍适用的礼品卡,因为只要居民所得到的是现金补偿,那么这些居民就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是把他们的补偿款集中起来去修建公园、图书馆和游乐场(如果这样做可以使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话),还是选择把这笔钱用于私人消费。
然而,这种逻辑缺失了公民奉献这层含义。相较于给私人现金这种补偿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可以说是对公共工程所引起的危险和不便的更合适的补偿方式,因为公共物品承认了有关公共工程地点的决策所设定的公民负担和公共奉献精神。政府部门因居民同意在他们的城镇修建新的飞机场跑道或垃圾填埋场而给他们金钱,可被视作是在贿赂他们默认对其社区的贬损。但是,新的图书馆、游乐场或学校可以说是通过加强社区和尊重其公共精神的方式,来补偿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的公民奉献精神。
人们业已发现,在不如核废料那么意义重大的其他情境中,金钱激励措施也会排挤公共精神。每年,在某个指定的“捐赠日”里,以色列的高中生会为慈善事业(如癌症研究、援助残疾儿童等事项)挨家挨户去募捐。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当时做了一项实验,以发现金钱激励措施对这些高中生的动机所产生的影响。
两位经济学家把学生分成3个小组。他们给第一组的学生做了一则关于慈善事业重要性的简短的激励性演讲,接着便让这些学生募捐去了。他们给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不仅做了同样的演讲,而且还根据这些学生所筹集的捐款数额给他们以金钱奖励:第二组学生奖励1%,第三组学生奖励10%。当然,给学生的奖励不会从慈善捐款里出,而来自其他地方。 [30]
你认为哪组学生募集到的钱会最多呢?如果你猜的是没有酬劳的那组学生,那么你猜对了。无酬劳的学生所筹集的捐赠额要比那些获得1%佣金的学生所筹集到的捐赠额多55%。那些获得10%佣金的学生要比获得1%佣金的那组学生做得好,但还是没有那组完全没有酬劳的学生做得好。(无酬劳的志愿者们所筹集的捐款额要比那些可拿到高佣金的学生所筹集的捐款额高出9%。) [31]
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呢?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如果你打算用金钱激励措施去鼓励人们,那么你就应当要么“给予足够多的钱,要么一分钱都不给”。 [32] 尽管支付足够多的钱确实有可能会使你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关于金钱是如何把规范排挤出去的教训。
这项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样一个假定,即金钱会激励人们工作。因为那组获得10%佣金的学生当时筹集的捐款额毕竟要多于那组获得1%佣金的学生。但是这里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组可获得酬劳的学生落后于那组无酬劳的学生呢?这极可能是因为付钱让学生去做好事改变了筹集捐款这种活动的性质。在发放佣金的情况下,挨家挨户筹集慈善捐款在当时已经不完全是在履行一种公民职责,而更多地为了赚取佣金。金钱激励措施把一种充满公共精神的活动变成了一份挣钱的工作。对以色列的高中生而言,就像对瑞士小山村的村民一样,市场规范的引入把他们的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了出去,至少是挫伤了它们。
一个相似的教训也可以见之于这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所做的另一项著名的实验——一项涉及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正如我们已然见到的那样,对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科以罚款,迟接孩子的父母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事实上,迟接孩子现象的发生概率几乎翻了一番。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把这种罚款视作他们愿意支付的酬金。事实还不仅如此:大约12个星期以后,当以色列托儿所取消罚款做法时,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保持着新高的势头。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 [33]
核废料贮存点、慈善资金募集活动和迟接日托孩子这3个事例,阐明了把金钱引入非市场环境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把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出去的方式。市场关系的腐蚀效应有时候会强大到足以压倒价格效应:提供金钱激励措施让人们接受有潜在危险的核废料设施、让学生挨家挨户去筹集慈善捐款或者让迟到的父母准时去接孩子,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人们这样做的意愿。
我们为什么会为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呢?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金钱方面的理由,另一个是伦理方面的理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比如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大交易。社会规范会激励人们去做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而没有社会规范的激励,我们就得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行为。如果你不得不依赖金钱激励措施去使相关社区接受核废料设施,那么你就必须支付远远多于你依赖居民的公民义务感所需要的费用。如果你不得不雇用学生去筹集慈善捐款,那么你就必须支付比10%佣金还多得多的费用,去获得与无偿学生凭借公共精神得到的相同的结果。
但是,仅仅把道德规范和公民规范当作激励人们的有效经济方式,会忽略这些规范的内在价值。(这就像我们把现金礼物的恶名视为一种会妨碍经济效率但却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评判的社会事实一样。)完全依赖现金支付来促使居民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做法,不仅在经济上是昂贵的,而且也具有腐蚀性。这种做法其实既忽视了说服,也忽视了居民在对这种设施将会产生的风险以及整个社会对这种设施的需求进行认真商议以后表示的同意。同样,给学生现金让他们在捐赠日筹集捐款,不仅会增加募集捐款的成本,而且也是对他们的公共精神的不尊重和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侵损。
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市场会改变其所调控的物品和社会惯例的性质。近年来,最早强调市场对非市场规范的腐蚀作用的学者之一是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他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顾问。弗雷德·赫希在1976年出版了《增长的社会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就在同一年,加里·贝克出版了他那部颇有影响力的论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而在该书出版的3年后,撒切尔夫人当选了英国首相。弗雷德·赫希在其著作中挑战了这样一个假定,即不论某种物品是由市场提供的,还是以某种其他方式提供的,该物品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弗雷德·赫希论辩说,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他所称之为的“商业化效应”(commercialization effect)。所谓“商业化效应”,赫希指的是“对专门或主要以商业目的而非一些其他原因供应这种产品或活动的特征所产生的影响,而这里的一些其他原因则包括非正式交易、相互性义务、利他主义或出于情爱、服务感或义务感”。一个“共同的假定(几乎总是一种隐含的假定)是,商业化过程对这种产品没有影响”。赫希指出,这种错误的假定是在当时日益盛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中凸显出来的,而在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中,也包括加里·贝克和其他经济学家尝试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适用于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努力。 [34]
两年后弗雷德·赫希去世了,享年47岁,因而他没有机会详尽阐释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他的《增长的社会极限》一书在那些拒绝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的趋势,并拒绝助长这种趋势的经济学逻辑的学者中成了一部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在前文讨论的3个实证案例,都支持弗雷德·赫希的这个洞见,即市场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会把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近来,其他从事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也不断发现了有关商业化效应的进一步证据。
比如,在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位经济学家丹·阿雷利(Dan Ariely)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付钱让人做某事,相较于请他们无偿做该事,可能会让他们激发出较少的热情——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的时候。丹·阿雷利讲述了一件能够证明其发现的现实生活逸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向一些律师咨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以每小时30美元的优惠价格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这些律师拒绝了。后来,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问这些律师是否愿意免费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时,他们却同意了。当这些律师弄清楚他们是被邀请去参加一种慈善活动而非某种市场交易的时候,他们便以慈善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35]
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这种商业化效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些研究强调了内在动机(比如手头工作的道德信念或兴趣)与外在动机(比如金钱奖励或其他有形的酬劳)之间的区别。当人们从事一项他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时,给他们金钱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通过贬低或“排挤”他们的内在兴趣或承诺而弱化他们的动机。 [36] 规范经济学理论把所有的动机(不论这些动机的性质或渊源)都解释成偏好,并且假定它们都具有加法性质。但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金钱所具有的腐蚀效应。
这种“排挤”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表示了怀疑,其中包括运用金钱激励措施来鼓励人们在教育、健康保健、工作场所、志愿者协会、公民生活和其他内在动机或道德承诺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中的表现。布鲁诺·费莱(研究瑞士核废料贮存点问题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雷托·吉根(Reto Jegen)把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排挤社会规范现象对经济学的意义概括如下:“可以说,‘排挤效应’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异常事例之一,因为它表明了与最基本的经济学‘法则’(即加大金钱激励措施会增加供应)相反的事例的存在。如果排挤效应是有道理的,那么加大金钱激励措施就会减少而非增加供应。” [37]
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最著名的实例,也许是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所做的一项有关献血的经典研究。在其1970年出版的《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在英国,所有用来输血的血液都来自于无偿献血者,而在美国,部分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者,部分血液是由商业血液银行从一些愿意把卖血作为一种挣钱途径的人(一般是穷人)那里买来的。理查德·蒂特马斯赞同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反对将人的血液当作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一种商品。
蒂特马斯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仅从经济和实际的角度来看,英国血液采集系统要比美国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他论辩说,尽管经济学假定市场是高效的,但是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却导致了血液的长期短缺、浪费、较高的成本和存在被污染的较大风险。 [38] 此外,蒂特马斯还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来反对血液的买卖。
蒂特马斯反对血液商品化的伦理观点为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反对市场的两种论点(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部分观点认为,血液市场剥削了穷人(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他指出,美国以营利为目的的血液银行,乃是从极需“快钱”的贫民区居民那里采集大量血液。血液的商业化使得更多的血液“来自于穷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人员、黑人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他在其论著中还写道:“正在出现一个由受剥削的血液高产人群组成的新阶层。”血液“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似乎是美国血液银行系统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 [39]
不过,理查德·蒂特马斯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把血液变成一种市场商品的做法,会侵蚀人们献血的义务感、消减人们的利他精神,并会破坏作为社会生活的现实特征的“礼物关系”(即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审视了美国的情况以后,他对“近年来美国人志愿献血率的下降”深感遗憾,并认为这是美国商业血液银行兴起所导致的结果。“血液的商业化和血液中的利润已经把志愿献血者赶跑了。”理查德·蒂特马斯指出,一旦人们开始把血液视为可以日常买卖的商品,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感觉到有要献血的道德责任。在这里,他所揭示的正是市场关系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效应,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个说法。大范围的血液买卖,终结了无偿献血这一做法。 [40]
蒂特马斯所担忧的不仅是人们献血意愿的减少,而且也包括人们献血行为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道德意义。献血精神的式微不仅会对所收集血液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还会使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贫瘠的现象。“利他精神在人类某一活动领域的式微,也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在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中的态度、动机和关系等方面发生类似的变化。” [41]
尽管基于市场的系统并不会阻碍任何基于自愿的主动献血,但是充斥于该系统的市场价值观却对献血规范施加了一种腐蚀性影响。“社会构建和组织其社会制度(尤其是健康和福利制度)所依靠的各种方式,既能够激励也能够挫败人们的利他心;这类社会制度既能够产生凝聚力,也能够导致疏离感;它们能够让‘礼物的主旨’(即对陌生人的慷慨)在社会群体间和代际间广为传播。”蒂特马斯所担忧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驱动的社会有可能会对利他主义构成极大的伤害,进而会被认为有可能侵害人们应当享有的自由。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血液和捐赠关系的商业化压制了人们对利他主义的表达,而且也侵蚀了人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 [42]
理查德·蒂特马斯所著《礼物关系》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在众多的批评者当中,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也名列其中。阿罗是当今这个时代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阿罗与倡导放任市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完全不同。他在其早期的论著中就已经对健康保健市场中的不完善问题进行过分析。但是,阿罗却强烈反对蒂特马斯对经济学和市场观念的批判。 [43] 在这样做的时候,阿罗援引了市场信念的两大关键原则——即经济学家常常宣称但却甚少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有关人性和道德生活的两个假设。
市场信念的第一个原则认为,把某种行为商业化并不会改变这种行为。基于这个假设,金钱绝不会腐蚀非市场规范,而且市场关系也绝不会排挤非市场规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赞同把市场扩展至生活所有方面的主张就很难抵制了。这是因为:如果把先前非交易的物品变成可交易的物品,那么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损害。那些想买卖该物品的人能够买卖该物品,从而增加这些人的功利,而那些认为该物品为无价之物的人则有不买卖该物品的自由。根据这种逻辑,允许市场交易可以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使一些人受益——即使拿来买卖的物品是人的血液。正如阿罗所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家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市场的创建增加了个人的选择范围,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于是,如果我们给自愿献血系统再增加一种卖血的可能选择,那么我们只是扩展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而已。如果他从献血当中得到了满足,那么人们可以论辩说,他可以继续献血,因为他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害。” [44]
阿罗的这种论证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血液市场的创建并没有改变血液的价值或血液的含义。血液还是血液,而且它仍将服务于维持生命这个目的,而不论这些血液是人们捐献的,还是买来的。当然,这里所涉及的物品不仅是血液,而且也包括出于利他主义精神的献血行为。蒂特马斯赋予激发人们献血的慷慨品格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但是,阿罗却质疑说,即使这种做法会因为引入市场而遭到侵损,那么“为什么血液市场的创建就肯定会减损献血行为所隐含的利他主义精神呢?” [45]
答案是,血液的商业化会改变献血的含义。试想,在一个血液可以正常买卖的世界里,你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献一品脱血液是否还是一种慷慨之举呢?或者说,献血这种做法是否会剥夺穷人将卖血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劳动呢?如果你想为献血做出贡献,那么你亲自去献血还是直接捐款50美元(这50美元可以被用于从需要这笔钱的流浪汉那里多购买一品脱的血液)更好呢?如果一个可能的利他者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罗对蒂特马斯的批判中所隐含的第二个市场原则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其要点是,我们不应当过分依赖利他主义、慷慨、团结或公民职责,因为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资源。依赖自利的市场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尽有限的美德资源。因此,比如,如果我们在血液的供应上依赖公众的慷慨,那么他们在其他的社会目的或慈善目的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慷慨了。然而,如果我们运用价格体系来运作血液供应系统,那么在我们真正需要人们的利他动机时,我们就可以运用他们未曾减少的利他动机。阿罗在其《礼物与交易》(Gifts and Exchanges)一文中写道:“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也不想过分地依赖那种用道德伦理去替代自利的做法。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讲最好的情况是,对伦理行为的要求只能有限地适用于价格体系失效的那些情形……我们不想鲁莽地把利他动机这类稀缺资源都用尽。” [46]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经济的美德观念(如果有的话)是如何为那种把市场扩展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传统上由非市场价值观所调整的那些领域)的做法提供进一步根据的。如果利他主义、慷慨和公民美德的供应(像化石燃料的供应一样)就好像是自然给定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保护好它。因为我们用得越多,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越少。根据这个假设,更多地依赖市场、更少地依赖道德规范,乃是保护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这个理念的经典表述乃是由丹尼斯·罗伯逊爵士(Sir Dennis H. Robertson)于195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出来的。丹尼斯·罗伯逊爵士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且曾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生。罗伯逊演讲的题目是一个问句,即“经济学家节约什么?”他试图证明,尽管经济学家迎合人们的“进取本能和占有本能”,但是他们也服务于一种道德使命。 [47]
罗伯逊在演讲一开始就承认,经济学所关注的并不是人类最高贵的动机,而是人类的获益欲望。“只有专职或业余布道士”才极力宣扬比较高尚的美德:利他主义、仁慈、慷慨、团结和公民职责。“经济学家的卑下角色(而且常常是令人反感的角色)就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把布道士的使命减约到人们可以做到的程度。” [48]
那么,经济学家如何帮助人们呢?通过推进那些尽可能依赖自利而非利他或道德考量的各种政策,经济学家使得社会不再滥用稀缺的美德资源。罗伯逊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为节约……爱这种稀缺资源(即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做出极大的贡献。” [49]
对于那些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讲,这种理解高尚美德的方式是怪异的,甚至是牵强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爱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使用而耗竭,反而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扩展。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对恩爱夫妻的情形。如果这对恩爱夫妻在其一生中都为了积攒他们的爱而不在意对方,那么他们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呢?如果这对夫妻更多地向对方表示爱情,那么他们之间的爱难道不会强化反而会减少吗?如果他们以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对待彼此,即把他们的爱一直保存到他们真正需要爱的时候才使用爱,那么这会使他们过得更好吗?
我们也可以对社会团结和公民美德提出与上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通过下述方式来努力保有公民美德,即在他们的国家需要召唤他们为共同善做出牺牲之前一直让公民去购物?或者说,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否会因为人们不使用它们而萎靡减少?许多道德家都持第二种观点。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我们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我们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 [50]
卢梭也持一种类似的观点。国家向其公民要求得越多,公民对国家的奉献也就越大。“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城市中,每个人都乐于参加集会。”而在一个丑恶政府的统治下,没有人会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没有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国家的关切之事本是极令人感兴趣的”。经由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构,而非耗竭。卢梭指出,事实上,就公民美德而言,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关注的主要事务,而且相较于为人们工作,他们宁愿为金钱工作,那么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不远了。” [51]
罗伯逊以一种轻松且思辨的方式阐述了他的观点。但是,他那种认为爱和慷慨乃是因为使用而会耗竭的稀缺资源的观点,却一直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想象施加了一种强有力的钳制,即使他们没有公开赞同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官方教科书中的一项原理(如供需法则那样)。任何人都没有从经验层面证明过这个观点。它更像是一则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赞同的谚语,即一种民间智慧。
在罗伯逊演讲的近半个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受邀在哈佛纪念教堂(Harvard’s Memorial Church)做晨祷演讲。他选择了“经济学能够为道德问题的思考贡献什么”(economics can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moral questions)作为他晨祷演讲的主题。他指出,经济学“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对于道德的重要性极少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 [52]
萨默斯指出,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即对个人自己设定的需要、品位、选择和判断的尊重”。接着,他为共同善提供了一种规范的功利主义解释,也就是把它解释为人们的主观偏好的总和:“许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善是许多个人对他们自己幸福的评估的集合,而不是某种可以撇开这些个人偏好并只根据某种独立的道德理论而予以评估的东西。”
一些研究者主张抵制血汗工厂所生产的物品,但是萨默斯却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来证明他的分析进路:“我们都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补偿深感哀叹。然而,肯定有某种道德力量在支撑这种状况,即只要这些工人是自愿受雇的,那么他们便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来做这份工作的。难道减少个人的选择才是尊重吗,才是慈善吗,甚或是关切吗?”
在晨祷演讲的最后,萨默斯对那些批评市场依赖自私和贪婪的人做出了如下回应:“我们所有的人只拥有那么多利他心。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利他心是一种需要保护的贵重且稀缺的物品。也许通过下述两种做法把这种稀缺物品保护起来要好得多:第一,设计一种可以通过自私的个人来满足人类欲求的系统;第二,把保护下来的利他心用于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这个世界上市场无法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
萨默斯的观点乃是对罗伯逊那番名言的重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伯逊那番名言的萨默斯版甚至要比阿罗版更为激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利他心的大肆挥霍,不仅会大大耗费掉可用于其他公共目的的利他心,甚至还会减少我们为家人和朋友所预留的利他心总量。
上述经济的美德观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奉,并推动市场向其本不属于的那些领域扩展。但是,这种隐喻却是误导性的。利他心、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并不像那些由于使用而会耗竭的商品。它们更像是那种由于锻炼而会生长并变得发达的肌肉。由市场驱动的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会使利他心、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这些美德失去活力。为了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然一新,我们需要更奋发地“锻炼”或使用这些美德。
48岁的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蒂尔顿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助理经理。一天,他在帮助一名顾客将电视机搬上她的轿车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并倒地不起。一周之后,他去世了。根据他的人寿保险单,保险公司为他的死亡偿付了约30万美元。但是这笔钱却没有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而是给了沃尔玛超市,因为这家超市在先前就已经为赖斯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把自己指定为受益人。
[1]
赖斯的遗孀维基·赖斯(Vicki Rice)在得知沃尔玛超市得到了这笔意外之财后感到非常愤怒。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从她丈夫的死亡中获益?赖斯生前每天都要为这家公司工作很长时间,有时候每周要工作长达80个小时。她说:“他们先是拼命使用迈克尔,然后毫不费力地得到了30万美元。这太不道德了。” [2]
按照赖斯夫人的说法,无论是她还是她的丈夫,都对沃尔玛公司曾为她丈夫办理人寿保险一事毫不知情。当她得知这份人寿保险单后,她便把沃尔玛告上了联邦法庭,要求把这笔钱判给她的家庭,而不是给沃尔玛。她的律师论辩说,公司不应当从其员工的死亡中获益:“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拿其雇员的生命进行赌博的行为,绝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3]
沃尔玛的一位发言人承认,公司持有其数千名雇员的人寿保险单——这些人并不只是助理经理,甚至也包括维修工这样的员工。但是他也否认了这种做法就是要从员工的死亡中获益的说法。他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从同事的死亡中获益。我们在这些员工身上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而且“如果他们一直活着的话”,那么公司只能继续支付他们的保险费。这位发言人论辩说,在迈克尔·赖斯的案例中,保险赔付的这笔钱并不是一份令人高兴的意外所得,而是对培训赖斯以及现在重新雇人替换他的成本的一种补偿。“他曾经接受过相当多的培训,并且获得了不付出代价便无法复制的经验。” [4]
公司为其首席执行官和高层行政主管办理人寿保险、用以抵消他们一旦去世而需雇人替换他们所产生的高昂成本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惯例。按照保险业的说法,公司对它们的首席执行官享有一种“可保权益”(insurable interest),而且这也是法律认可的。但是公司为普通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相对而言则是新近才出现的。这样的保险在保险业中被称为“普通员工保险”(Janitors insurance)或者“死亡佃农保险”(dead peasants insurance)。直到最近,这种保险在美国大多数州还是不合法的;这些州认为,公司对它们的普通员工生命不享有可保权益。但在20世纪80年代,保险业成功地游说了大多数州的立法机构,让它们放宽了对保险法的限制,允许公司为它们的所有雇员(从首席执行官到收发室职员)购买人寿保险。 [5]
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公司已耗资数百万美元来投保公司员工的人寿保险(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简称COLI),并创造了一个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死亡期货产业(death futures industry)。为员工购买保险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美国雀巢公司(Nestlé USA)、必能宝公司(Pitney Bowes)、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沃尔玛、迪士尼(Walt Disney)和温迪克西连锁超市(Winn-Dixie supermarket chain)。这些公司在当时之所以愿意进行这种病态的投资,乃是因为这样的投资可以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正如死亡保险金在传统的终身人寿保险业务中是免税的,普通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所产生的年度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 [6]
几乎没有员工意识到他们的公司已经给他们的人头标价了。大多数州都没有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需通知雇员本人,也没有要求公司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征得员工的允许。而且大多数公司为员工购买的人寿保险甚至在员工辞职、退休或者被辞退后也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仍能获得离开公司多年以后去世的员工的死亡保险金。公司通过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来跟踪了解它们之前员工的死亡状况。在一些州,公司甚至还可以办理其员工的孩子与配偶的人寿保险并获取死亡保险金。 [7]
普通员工保险在大银行中曾是非常流行的,这些银行包括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银行还曾想过除了它们的员工之外,给它们的存款人和信用卡持有人办理人寿保险事项。 [8]
普通员工保险这项繁荣的生意因《华尔街日报》在2002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一名29岁的男子在1992年死于艾滋病,他的死亡使一家公司得到了33.9万美元的死亡保险金,而他的家庭却分文未得。这家公司就是他曾经短暂工作过的一家音乐制品商店的所有者。另一篇文章讲述了得克萨斯州一名20岁便利店职员的遭遇,他在该店遭抢劫的过程中被枪击身亡。拥有这家便利店的公司为这名年轻男子的遗孀和孩子支付了6万美元,以便让他们不再提起任何诉讼,但却没有向他们透露公司已经因该男子的死亡而得到了25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这一系列文章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无情但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事实,即“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一批人寿保险赔偿金中,有一些并没有给遇难者的家庭,而是给了他们的雇主”。 [9]
截至21世纪的头几年,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承保了数百万名员工的生命,其总额达到了全部人寿保险销售额的25%~30%。2006年,美国国会曾试图制定一项法律来限制普通员工保险业务,该项法律要求这种业务需征得雇员的同意,并将公司拥有的保险限制在公司1/3薪酬最高的劳动力的范围内。到2008年,仅美国各家银行就持有其员工的1 220亿美元的人寿保险。普通员工保险向美国各家公司的扩展,已然改变了人寿保险的意义和目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系列文章得出结论:“普通员工保险所展现的无异于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人寿保险如何从一种丧失亲人的安全网络演变成了一种公司财政策略。” [10]
公司是否应当可以从其雇员的死亡中获益?甚至保险业中的一些人士也都发现这种做法令人反感。“美国全美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TIAA-CREF)是一家从事退休与财务服务的大公司,它的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比格斯(John H. Biggs)将这种做法称为“一种似乎总会令我感到厌恶的保险形式”。 [11] 但是它究竟错在哪里呢?
最直白的反对意见是一种实践性的意见:允许公司因其员工死亡而获得经济利益的做法,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几无裨益可言。相反,一家缺乏资金的公司如果可以因其员工的死亡而得到数百万美元,那么它就会滋生一种反向的动机,即在健康与安全措施方面偷工减料。当然,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公司都是不会公然依照这种动机行事的。公司故意加速其雇员的死亡,乃是一种犯罪。允许公司为其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并没有为它们发放杀害员工的许可证。
然而据我猜测,那些对普通员工保险极其反感的人所主张的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反对意见,已经超出了那种实践性的风险观,即肆无忌惮的公司有可能在工作场所乱扔致命危险品或者对各种危险熟视无睹。这种道德性的反对意见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人们是否必须接受它呢?
这种反对意见很可能与同意的缺失有关。如果你得知你的雇主在你不知情或者未同意的情况下为你办理了人寿保险,你会作何感想呢?你有可能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是你有理由抱怨吗?如果这项保险的存在对你并无伤害的话,那么你的雇主为什么有通知你这件事或者征得你同意的道德义务呢?
普通员工保险毕竟是双方当事人——购买此项保险(并成为受益人)的公司与出售此项保险的保险公司——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交易。员工并不是这项交易的当事人。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科凯集团(KeyCorp)的发言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雇员并没有支付保险费,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向他们透露这项保险的细节。” [12]
一些州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它们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办理保险之前一定要征得员工本人的同意。当公司向员工征得许可的时候,它们一般都会向员工提供一份适度的人寿保险收益作为诱饵。沃尔玛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办理了大约35万名员工的保险,它向那些同意由它办理保险的员工提供一笔免费的价值5 000美元的人寿保险收益。大多数员工都接受了这个报价,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的5000美元保险收益与该公司将从他们的死亡中获取的数十万美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13]
然而,同意的缺失并不是可以用来反对普通员工保险的唯一的道德性反对意见。即便在员工同意此类方案的情形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在道德上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指公司对待那些被参保员工的态度。公司在制造使员工的死亡比活着更有价值的情形中,实际上是把他们客体化了。公司把员工看成一种商品期货,而不是雇员——他们对公司的价值在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那种人。一种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指出,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扭曲了人寿保险的目的;人寿保险曾经是一种家庭安全的渊源,而现在却变成了公司减免税收的一项举措。 [14] 我们很难理解,税收制度为什么应当鼓励公司为其员工的死亡投资数十亿美元,而不是为提供服务和生产商品进行投资。
为了检视上述各种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在道德上颇为复杂的人寿保险做法。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由艾滋病的流行而引发的。它在当时被称作保单贴现行业(viatical industry),是一个由艾滋病人群和其他被诊断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拥有的人寿保险单所构成的市场。它的运作方式如下:假设某个拥有10万美元人寿保险单的人被医生告知自己只有一年的寿命。再假设他现在需要钱来进行治疗,或许只是为了在他所剩无几的短暂时光中好好地生活。于是,一位投资者提出以折扣价——比如5万美元——从这位病人手中买下这份保单,并且替他缴纳年度保险费。在这位保单原始持有人去世的时候,该投资者便可以得到10万美元。 [15]
无论怎么看,这似乎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位垂死的保单持有人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现金,而这位投资者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假设保单持有人按预定时间死亡。但是这种交易有一种风险:虽然这种保单贴现投资可以确保投资人得到一笔确定的死亡赔付金(在上述事例中是10万美元),但是回报率却要取决于保单持有人活多长时间。如果他按照预期那样在一年之内去世了,那么这位花5万美元买下10万美元保单的投资者就会大赚一笔,也就是说100%的年利润(这里要减去他所支付的保险金和付给安排此项交易的保险经纪人的费用)。如果这个人又活了两年,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必须要为同等数量的保险费赔偿金等待两倍的时间,因此他的年度回报率也要减半(这里还不算额外的保险费支出,而这项支出还会使回报变得更少)。如果这位病人奇迹般地获得康复并存活了很多年的话,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可能一无所获了。
当然,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就保单贴现而言,这种金融风险产生了一种在其他大多数投资中都没有的道德复杂性:投资者肯定希望卖给他人寿保险的那个人死得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这个人活得越久,自己获得的回报率也就越低。
毋庸赘言,保单贴现行业会竭力弱化其生意中残忍的一面。保单贴现经纪人把他们的任务描述成:为身患绝症的人提供财力,使他们能够以相对舒适和有尊严的方式度过剩余的时光。[“保单贴现”(viatical)这个词就源于拉丁语的“航海”(voyage)一词,该词特指为古罗马官员出海航行而提供的资金和补给品。]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如果被保险人立即死亡,那么投资者是有利可图的。劳德代尔堡保单贴现公司的主席威廉·斯科特·佩奇(William Scott Page)就说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蔚为可观的回报,但是在人们活得较长的情况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恐怖的事情。这就是保单贴现协议令人刺激的地方。在预测某人死亡时间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精确的科学方法。” [16]
在这些“恐怖的事情”中,有一些导致了诉讼:不满的投资者状告经纪人卖给他们的人寿保险单并没能按预期那样迅速“到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发现延长了成千上万名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但是这项发现却打乱了保单贴现行业的如意算盘。一家保单贴现公司的行政主管对延长患者生命药物的负面作用做了如下解释:“12个月的预期变成了24个月,这会严重破坏你的回报。”1996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技术的突破,导致了尊严合作有限公司(Dignity Partners, Inc.)——旧金山的一家保单贴现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4.5美元暴跌至1.38美元。很快,这家公司便停业了。 [17]
199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关于一位愤怒的密歇根投资者的故事,他在5年前购买了肯德尔·莫里森(Kendall Morrison)的人寿保险。莫里森是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纽约人,当时他已病入膏肓。多亏了前述这种新药的发明,莫里森恢复到平稳的健康状况,而这让那位投资者大失所望。莫里森说:“以前,我从未觉得有人希望我死掉。他们不停地给我寄这些联邦快件并给我打电话,好像在说‘你还活着吗’?” [18]
由于艾滋病的确诊不再是一种死亡判决,所以保单贴现公司便开始努力使它们的生意变得更加多样化,也就是把它们的业务扩展至癌症和其他绝症方面。美国保单贴现协会(the Vi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乃是这个行业的贸易协会,它的执行董事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就没有因艾滋病市场的低迷而屈服,反而对死亡期货生意给出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与艾滋病患者的人数相比较,患有癌症、严重心血管疾病和其他不治之症的人数更巨大。” [19]
与普通员工保险不同,保单贴现行业服务于一种明确的社会善,即为绝症患者的最后岁月提供财力支持。此外,被保险人的同意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尽管下面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即在某些情形中,绝望的患者有可能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无法为他们的人寿保险谈到一个公道的价格)。保单贴现的道德问题并不是它们缺少同意,而在于它们是在对死亡下赌注。这种赌博使得投资者与被其购买了人寿保险的病人的早日死亡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利益挂钩。
可能有人会回应说,保单贴现并不是唯一无异于死亡赌博的投资。人寿保险业也同样把我们的死亡变成了一种商品。但是这二者却是有区别的:就人寿保险而言,卖给我保险的公司是在赌我活,而不是在赌我死。我活得越长,它就赚得越多。就保单贴现而言,经济利益正好是反向的。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我死得越快,情况就越好。
为什么我应当担心投资者有点盼着我早死呢?只要投资者没有按其期望行事或者没有太频繁地打电话询问我的状况,也许我就不应当担心。这可能只是有点吓人,而无法从道德上加以反对。或者说,这里的道德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它对我的任何实际伤害,而在于它对投资者品质的腐蚀性影响。你会愿意靠着打赌某些人早点死而非晚点死来营生吗?
我猜想,即便是自由市场的狂热者在面对如下观点的含义时也会犹豫再三,即拿他人的死亡进行打赌的行为只不过是另一种生意罢了。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如果保单贴现生意在道德上与人寿保险具有可比性,难道它不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拥有同样的游说权利吗?如果保险业拥有为其在延长生命(通过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或禁烟政策)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那么保单贴现行业就不应当拥有为其在加速死亡(通过减少对艾滋病或癌症进行研究的联邦资助)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吗?据我所知,保单贴现行业并没有进行这种游说。但是,如果道德上允许人们对艾滋病或癌症患者会早点死而非晚点死的可能性进行投资的话,那么为什么推进有利于该目标的公共政策的做法在道德上却是不正当的呢?
保单贴现投资者沃伦·齐兹厄姆(Warren Chisum)是得克萨斯州一位保守党的立法议员和“著名的反同性恋战士”。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在得克萨斯州举行的恢复对鸡奸进行刑事处罚的运动,反对性教育,并投票反对援助艾滋病患者的项目。1994年,齐兹厄姆骄傲地宣称,他投资20万美元购买了6名艾滋病患者的人寿保险。他告诉《休斯敦邮报》(The Houston Post)说:“我打赌这会使我赚到不少于17%的利润,而且有时候还会更多。如果他们在一个月内就死掉的话,你知道,那这些投资就真的会大有回报了。” [20]
有些人指责这位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者投票支持那些他可以从中获得个人私利的政策。然而这项指控却被误导了;他的钱所追随的乃是他的信念,而非其他事情。这并不存在典型的利益冲突。它实际上是某种更糟糕的东西:一种在道德上扭曲的社会意识投资。
齐兹厄姆对保单贴现残忍面所持有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欢欣纯属例外。保单贴现的投资者几乎很少是由恶意驱动的。大多数投资者还是希望艾滋病患者能够身体健康和长寿的——除了那些已被投资的患者外。
在依靠人的死亡谋生方面,并非只有保单贴现投资者。验尸官、殡仪业者和挖墓者都是如此,但是却没有人在道德上谴责他们。几年前,《纽约时报》描绘了迈克·托马斯(Mike Thomas)的工作,这名34岁的男子是底特律某个县停尸房的“尸体收集者”(body retrievalist)。他的工作就是收集那些死亡者的尸体,并把他们运到太平间。他是按人头收费的,也就是说,他收集一具尸体收14美元。由于底特律的谋杀率很高,所以他从这项可怕的工作中每年大约能挣1.4万美元。但是当暴力事件减少时,托马斯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等着某人死亡。希望某人死亡。但是这个行当就是这样运作的。这也是我养活我的孩子的方式。” [21]
向尸体收集者支付佣金的做法也许是合算的,但是这也要承担一种道德成本。使尸体收集者的经济利益与其同胞的死亡相挂钩,有可能会使他的以及我们的道德情感变得麻木。就此而言,尸体收集者的工作有点像保单贴现生意,但在道德上却与之不同:虽然尸体收集者依靠他人的死亡维持生计,但是他不必希望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早些死掉。任何人的死亡对他来说都是可以的。
一种与保单贴现更为类似的行当被称为“死亡赌局”(death pool),这是一种骇人的赌博游戏。它于20世纪90年代在互联网上流行开来,几乎是在保单贴现行业盛行的同时。过去,有一种打赌谁会赢得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办公室赌局,而死亡赌局就是这种办公室赌局在网络上的翻版,只不过玩家们并不是打赌谁将在橄榄球比赛中获胜,而是竞相预测哪些名人会在某一特定年份死去。 [22]
许多网站都提供了这种病态游戏的各种版本,其名称有“食尸鬼赌局”(Ghoul Pool)、“死亡赌局”以及“名人死亡赌局”(Celebrity Death Pool)等。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叫作“僵尸网”(Stiffs.com),它于1993年举办了第一场游戏,并于1996年进入互联网。在缴纳15美元的参赛费后,参赛者要提交一份他们认为很可能在年底之前去世的名人的名单。猜得最准的那个人可以赢得3 000美元的头奖,第二名可获得500美元。“僵尸网”每年都可以吸引1 000多名竞猜者。 [23]
认真的玩家并不会轻易地作出选择,他们会先四处搜寻各种载有患病明星消息的娱乐杂志和小报。目前玩家偏爱下注的是莎莎·嘉宝(94岁)、葛培理(93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85岁)。其他受欢迎的死亡赌局选项则包括柯克·道格拉斯、玛格丽特·撒切尔、南希·里根、穆罕默德·阿里、鲁思·贝德·金斯伯格、斯蒂芬·霍金、艾瑞莎·富兰克林和阿里埃勒·沙龙。由于年迈的和生病的人物充斥着这些名单,因此一些游戏对那些成功预测很难猜到的死亡的名人还给予额外的积分奖励,例如戴安娜王妃、约翰·丹佛或者其他英年早逝的名人。 [24]
死亡赌局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早于互联网。据报道,这种游戏早在华尔街的商人中间流行几十年了。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所主演的警探哈利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虎探追魂》(The Dead Pool),就是关于依照名单神秘谋杀名人的死亡赌局故事。然而,互联网连同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市场的狂热,使得这种残忍的游戏又有了新的前景。 [25]
把赌注押在名人何时会死亡乃是一种娱乐活动,因为没有人靠它谋生。但是,死亡赌局也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保单贴现和普通员工保险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在警探哈利那个版本的游戏中,竞猜者欺骗并企图杀死死亡赌局所选择的名人,但是我们对此先撇开不论。拿某人的生命打赌并从他/她的死亡中获利的行为,有什么错吗?人们对此感到担忧。但是,假如赌徒并没有加速任何人的死亡,那么谁对此还有进行抱怨的权利呢?当一些与莎莎·嘉宝和穆罕默德·阿里从未谋面的人就他们两人何时会死亡这个问题进行打赌的时候,会使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吗?把某人升至死亡名单的榜首,或许带有某种侮辱的意味。但是我认为,这种游戏的道德庸俗性主要在于它所表达和弘扬的对死亡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一种轻薄和妄想的有害结合——玩弄死亡甚至对此迷恋不已。死亡赌局的参与者不只是在投注,而且还参与了一种文化。他们费时费力地去研究被他们押宝的人的预期寿命。他们对名人死亡有一种不体面的专注。死亡赌局网站充斥着著名人物生病的新闻和消息,进而鼓励这种残忍的痴迷。你甚至可以订购一种叫作“名人死亡呼叫”(Celebrity Death Beeper)的服务:每当一位名人死亡时,它都会给你发电子邮件或短信提醒你。“僵尸网”的经理凯利·巴克斯特(Kelly Bakst)说,参与死亡赌局的活动“真的会改变你看电视和关注新闻的方式”。 [26]
同保单贴现一样,死亡赌局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们做的是一种病态的买卖。但是与保单贴现不同的是,它们并非服务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严格来说,它们就是一种赌博,一种获利和娱乐的来源。尽管死亡赌局令人生厌,但是它们还很难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道德问题。在各种恶的排序中,它们还只是小恶而已。但是,人们之所以对它们感兴趣,乃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极限状况,揭示了保险业在一个市场驱动的时代里的道德命运。
人寿保险一直都是一体两面的:既是一种为了共同安全的风险分担,也是一种无情的赌注(即一种针对死亡的套购保值措施)。这两个方面共存于一种不稳定的联合之中。由于缺失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人寿保险所具有的那个赌博面,有可能吞没最初证明人寿保险正当性的那个社会目的。如果这个社会目的被遮蔽或者丢失的话,那么那些将保险、投资与赌博区分开来的脆弱界线也就荡然无存了。人寿保险从一种为亡者的亲属提供安全保障的制度,先是转变成了另一种金融产品,最终则退化成了一种针对死亡的赌博。这种赌博除了为那些玩家提供乐趣和利益之外一无是处。尽管死亡赌局看起来是轻浮的和无足轻重的,但它实际上却是人寿保险那个邪恶的孪生兄弟——即那种对社会之善毫无助益的赌注。
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和死亡赌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末期生命与死亡商品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这种趋势变得愈发严重了。然而,在我们考察这个问题在当下的状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人寿保险从一开始就一直使人们感觉到的那种道德忧虑。
我们通常都认为保险和赌博是对风险的不同回应方式。保险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而赌博则是一种投机风险的方式。保险与审慎有关,而赌博则与投机有关。然而,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线一直都是易变的。 [27]
在历史上,为生命保险与拿生命打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很多人都认为人寿保险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人寿保险不仅产生了一种谋杀的动机,而且还错误地给人的生命明码标价。几个世纪以来,人寿保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被禁止的。一位法国的法学家在18世纪写道:“人的生命不能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而且那种认为死亡应当变成一种商业投机来源的观点也是可耻的。”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都没有人寿保险公司。直到1881年,日本才出现了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由于缺乏道德正当性,“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之前都没有发展人寿保险”。 [28]
英国是一个例外。从17世纪晚期开始,船主、经纪人和保险商就聚集在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里——即当时的一个海事保险中心。一些人来这里为他们的船只安全返航和货物投保。另一些人来这里则是为了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一些生命和事件下注。很多人都办理了并不属于他们的船只的“保险”,期望这些船只在海上沉没以便获利。随着保险商充当起了博彩业者,保险业也就与赌博混杂在一起了。 [29]
英国的法律并没有对保险或赌博进行限制性规定,这两者在当时几乎是无法区分的。18世纪,保险“保单持有人”把赌注押在选举结果、议会的解散、两名英国贵族被杀的可能性、拿破仑的死亡或被擒以及女王在60周年庆典前几个月里的寿命等事件上。 [30] 另一些受欢迎的投机赌博对象,即所谓保险的赌博部分,包括围攻和军事战役的结果、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被大量投保的生命”,以及国王乔治二世是否会从战斗中生还等事件。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1715年8月患病时,英国驻法国大使就打赌这位太阳王活不过当年9月。(结果这位大使赌赢了。)“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通常都成了这些赌博业的押注对象”,而这就相当于当今网络死亡赌局的一个早期版本。 [31]
一次特别无情的人寿保险赌博与800名德国难民有关,他们在1765年被带到英国,然后被遗弃在伦敦的郊区,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于是,劳埃德咖啡馆的投机者和保险商就打赌这些难民中有多少人会在一周之内死去。 [32]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样一种赌博在道德上是骇人听闻的。但是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它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假如这些打赌者并不对这些难民的困境负责的话,那么他们拿这些难民多久会死亡来打赌又有什么错呢?打赌双方通过这场赌博都获益良多;而如果他们不玩这场赌博,那么经济逻辑会确定地告诉我们,他们就不会获益。那些对这场赌局毫不知情的难民,也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受到伤害。最起码,这就是毫无约束的人寿保险市场的经济逻辑。
如果我们可以反对死亡赌博的话,那么我们所依据的理由就肯定是超越市场逻辑的,即这些赌博所表达的那些毫无人性的态度。就赌博者自己而言,对他人的死亡和苦难毫不在意的漠视乃是其恶劣品质的标志。对整个社会而言,此类态度以及鼓励这些态度的制度,都是粗俗与堕落的。正如我们在其他商品化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对道德规范的腐蚀或排挤,就其本身而言,可能并不是人们拒绝市场的充分理据。但是,既然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赌的行为,除了提供利益和卑鄙的娱乐之外对任何社会之善毫无助益,那么这种活动的堕落品质就为人们严格控制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英国猖獗的死亡赌博,促使公众愈发强烈地反对这种令人讨厌的做法。此外,还有另一个限制它的理由。尽管人寿保险越来越被视作是养家糊口之人保护他们家庭免遭贫困的一种审慎方式,但是它却因为与赌博连在一起而在道德上被败坏了。为了使人寿保险变成一种在道德上正当的生意,它就必须与金融投机划清界限。
最终,《1774年保险法案》(又被称作《赌博法案》)的颁布,使得人寿保险与金融投机划清了界限。该项法案禁止拿陌生人的生命进行赌博,并把人寿保险限定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被投保人的生命拥有一种“可保权益”。由于一种没有约束的人寿保险市场在此前已经导致产生了“一种有害的赌博”,所以议会后来禁止了所有关于生命的保险,“除了这样一些情况,即投保人对被投保人的生死拥有相关利益”。历史学家杰弗里·克拉克(Geoffrey Clark)写道:“简而言之,这项《赌博法案》对人的生命可以被转变为一种商品的情形做出了限制。” [33]
在美国,人寿保险的道德正当性发展得很缓慢。直到19世纪晚期,它才被牢固地确立起来。虽然一些保险公司在18世纪就成立了,但是它们出售的大部分险种是火险和海事险。人寿保险遭遇到了“强大的文化抵制”。正如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所指出的,“将死亡变成一种商品的做法,侵害了一种捍卫生命神圣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价值体系”。 [34]
到了19世纪50年代,人寿保险业开始发展,但当时所强调的只是它的保护性目的,而其商业性的一面则被轻描淡写:“在19世纪晚期以前,人寿保险一直把自己包裹在宗教象征之中,避免使用经济学术语,而且它宣传的更多的是它的道德价值,而非它的金钱好处。人寿保险乃是被当作一种利他的、忘我的馈赠来买卖的,而不是被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来运作的。” [35]
后来,人寿保险的承办商在将其作为一种投资手段进行兜售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起来。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人寿保险的意义和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当人寿保险在交易时被当作一种保护寡妇和儿童的慈善制度来对待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存款与投资的工具并成为商业的一部分。对“可保权益”的界定也从家庭成员和亲属扩展到了商业伙伴和重要雇员。公司可以为它们的行政主管投保(尽管它们并不给它们的普通员工投保)。到了19世纪晚期,人寿保险的商业方式“鼓励生命保险严格地遵从商业目的”,从而把可保权益扩展到了“有经济利益关联的陌生人”。 [36]
人们对于把死亡商品化的做法在道德上仍感到犹豫。泽利泽指出,这种犹豫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人们对人寿保险代理人的需求。保险公司早就发现,人们并不愿意主动购买人寿保险。尽管人寿保险得到了人们的接受,但是“死亡也不能被转变成一种日常商品”。因此,这就需要有人去寻找客户,消除他们本能的犹豫,并说服他们相信这种产品的优点。 [37]
涉及死亡的商业交易的这种窘境,也解释了为什么保险推销员一直以来受到人们蔑视的原因。这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死亡关联太近。医生和牧师的工作也与死亡有关联,但他们却没有因为这种关联而名誉受损。人寿保险代理人之所以蒙受污名,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死亡‘推销员’,也就是靠着人们最糟糕的悲剧来营利谋生的人”。保险推销员的这种污名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尽管人寿保险代理人努力使他们的工作专业化,但是他们还是无法消除人们因其把“死亡当作生意”而产生的反感。 [38]
可保权益这项要件把人寿保险限定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投保的生命具有优先利害关系的人,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金钱关系。这有助于人们把人寿保险与赌博区分开来——人们再也不会只为了赚钱而拿陌生人的生命去打赌了。然而,这种区别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明确。因为法院的裁定认为,一旦你获得了一份人寿保险单(由可保权益所支持),你就可以任意处置它,包括将其卖给其他人。这项“转让”原则,正如它被称为的那样,意味着人寿保险就是一种与其他财产没什么两样的财产。 [39]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种出售或者“转让”某人的人寿保险单的权利。为法庭撰写判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承认了这个问题:赋予人们将其人寿保险单卖给第三方的权利,破坏了可保权益这项要件。这意味着投机者可以重新进入市场:“一份与被投保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寿保险合约,是一种纯粹的赌注,它使被投保人在终结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种险恶的反向利益。” [40]
这恰恰是几十年后保单贴现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份被肯德尔·莫里森(那名患有艾滋病的纽约人)卖给第三方的人寿保险单。对于购买这份保单的投资者而言,这份保单纯粹是一份关于莫里森会活多长时间的赌注。当莫里森没有很快死掉的时候,这位投资者发现自己倒是“在终结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种险恶的反向利益”。这就是那些询问莫里森身体状况的电话和联邦快件所具有的全部含义。
霍姆斯承认,对可保权益进行规定的全部要义就在于防止人寿保险演变成一种死亡赌博,即“一种有害的赌博”。但是他认为,这个理由还不足以阻止人寿保险的二手市场(它会把投机者从后门带回来)。霍姆斯得出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寿保险已经成为人们最认可的投资和自我强制储蓄的形式之一。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使人寿保险也具有财产的一般特性乃是可行的。” [41]
一个世纪以后,霍姆斯在当年所面临的困境变得更为严峻了。区分保险、投资和赌博的界线也都不复存在了。20世纪90年代的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和死亡赌局,只不过是个开端。今天,生命与死亡的市场已然挣脱了那些曾经限制它们的社会目的和道德规范对它们的约束。
假设有一种除了提供娱乐外还有其他作用的死亡赌局。设想有这么一个网站,它允许你可以不对电影明星的死亡进行押注,而对哪些外国领导人会遭暗杀或被推翻进行押注,或者对下一次恐怖袭击会发生在什么地方进行押注。让我们再假设这种赌局的结果将产生有价值的信息,而政府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保卫国家安全。2003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机构就曾提议创建这样一个网站。五角大楼把它称为“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Analysis Market);媒体则把它称为“恐怖活动期货市场”(terrorism futures market)。 [42]
这个网站是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发明,该局是一个负责为进行战争和搜集情报而开发创新技术的机构。这个网站的理念是,让投资者买卖有关各种情形(最初与中东有关)的期货合同。作为样本的情形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否会被暗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否会被推翻?以色列是否会成为生物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另一个样本问题是与中东无关的:朝鲜是否会发动核攻击? [43]
由于交易者必须用他们自己的钱来为他们的预测投注,因此那些愿意下大赌注的人很可能就是拥有最佳信息的人。如果期货市场可以很好地预测石油、股票和黄豆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们的预测能力用于预测下一次恐怖袭击呢?
关于这个赌博网站的新闻,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怒。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谴责这种期货市场,而国防部也迅速取消了这个计划。社会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对浪潮,部分是因为人们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起作用,但大部分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反感政府开设灾难事件赌局的前景。美国政府怎么可以怂恿人们利用恐怖活动和死亡来赌博和营利呢? [44]
参议员拜伦·多根(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质问道:“你是否能够想象:另一个国家设立了一个赌场,人们可以去那里……打赌一名美国政治人物是否会被暗杀?”参议员罗恩·怀登(俄勒冈州民主党人)与多根一起要求撤销这项计划,说它是“令人厌恶的”。怀登指出:“开设有关暴行和恐怖活动的联邦赌局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怪诞的。”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斯科尔(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将这个项目称为“不负责任的和粗暴的”。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相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提出我们应当用死亡来做交易。” 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说道:“它有点让人恶心。” [45]
五角大楼没有回应这些道德争论,反而发表了一项陈述该项目原则的声明,并论辩说期货交易不仅在预测商品价格方面一直是有效的,而且在预测选举和预测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成功方面也一直是有效的:“研究表明,市场乃是收集那些分散甚至隐蔽信息的极为高效的、有效的和及时的聚合器。期货市场已经证明了它很善于预测选举结果之类的事件,它们的预测往往比专家的观点还要准确。” [46]
一些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赞同这种观点。一位学者写道:“看到恶劣的公共关系毁掉了一种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情报分析工具,颇令人感到沮丧。”抗议的浪潮阻碍了人们对该项目的优点做出恰当的评价。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写道:“金融市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信息聚合器,而且也常常是比传统方法更好的预测者。”他们引证艾奥瓦电子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来说明问题,因为这家在线期货市场比民意测验更准确地预测了一些总统选举的结果。另一个案例则是橙汁期货市场。“相比于国家气象局,浓缩橙汁期货市场是佛罗里达州天气的更好的预报员。” [47]
市场预测优于传统情报搜集的一个地方在于:市场并不受制于官僚和政治压力所导致的信息失真。了解某些事情的中层专家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并把他们的钱投到他们确信的地方。这可以使某些原本被高层人士压制且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的信息曝光于大众。让我们回想一下伊拉克战争前中央情报局(CIA)所受到的各种压力——它必须得出结论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家独立的赌博网站对这个问题的怀疑,要大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的怀疑,后者曾宣称这种武器的存在就像是“灌篮得分”(slam dunk)那样确定无疑。 [48]
然而,支持恐怖活动期货网站的理据所依凭的则是一种信奉市场力量的更宏大且更宽泛的主张。随着市场必胜论进入高潮,该计划的捍卫者明确表达了一种伴随金融时代而形成的对市场信念的新认知:市场不仅是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最有效的机制,而且也是聚合信息与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期货市场的优点在于,它会“拨动、刺激和唤醒一个固执的情报界去认清自由市场的预测能力”。它会让我们打开眼界,使我们明白“决策理论家几十年来早已知晓的东西:事件的概率可以根据人们愿意下的赌注来测量”。 [49]
那种宣称自由市场不仅有效而且还有洞见力的主张,乃是不同寻常的。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个主张。一些经济学家论辩说,期货市场善于预测小麦的价格,但却在预测罕见事件(诸如恐怖袭击)方面力不从心。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就情报搜集而言,专家市场要比那些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市场更有效。人们还根据一些特别的理由来质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的这项计划:它是否会被恐怖分子所操纵?因为恐怖分子可能会为了从一场袭击中获利而参与“内幕交易”,或者有可能通过卖空恐怖活动期货来隐匿他们的计划。此外,如果人们知道美国政府会利用这种市场信息来阻止,比如,对约旦国王的暗杀并因此挫败他们的赌局的话,那么他们是否还真的会把赌注押在这个事件上呢? [50]
撇开这些实际问题不论,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反对意见,即政府开设的有关死亡和灾难的赌局是令人厌恶的。假设上述实际困难可以得到克服,而且恐怖活动期货市场也可以经由设计,而在预测暗杀和恐怖袭击方面比传统情报机构做得更好。那么对于用死亡和灾难进行赌博并营利的行为的道德厌恶感,是否还是抵制这种做法的充分理由呢?
如果政府提议开设一种“名人死亡赌局”的话,那么答案将一目了然:由于它不实现任何社会善,所以对于强化人们对他人的死亡与不幸的无情漠视或者(更糟糕的)极度痴迷的做法而言,也就无须多费口舌了。当诸如此类的赌博活动由私人经营时,它就更是坏到底了。肆无忌惮的死亡赌博腐蚀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派,政府应当加以阻止,而不是推进。
使恐怖活动期货市场在道德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状况的原因在于,与死亡赌局不同,它旨在做好事。假定它是有效的,那么它就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这就使它与保单贴现业务有些类似。在这两种情形中,道德困境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是否应当以道德为代价——使投资者的利益与他人的死亡与不幸紧密挂钩——来推进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为垂死之人的医疗需求提供财力支持或者阻止一场恐怖袭击?
一些人说:“是的,当然。”这是一位帮助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构想出这个计划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借着情报的名义,人们在撒谎、欺骗、偷盗和杀戮。相比于这些行为,我们的提议是非常温和的。我们只是从一些人那里拿了钱,然后根据谁的信息准确再把钱给另一些人罢了。” [51]
但是这个回答太随意了。它忽视了市场排挤道德规范的那些方面。当参议员们和社论作者们将恐怖活动期货市场斥责为“粗暴的”、“令人厌恶的”和“怪诞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为某人死亡下注并希望那个人死掉以便从中获利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丑陋的一面。尽管这种事情在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地方已然发生了,但是让政府去开设一个使其常规化的机构的做法在道德上却是堕落的。
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中,这或许是一种值得付出的道德代价。认为那些做法是堕落的观点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些观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种常常被市场热衷者所忽视的道德考量。如果我们确信恐怖活动期货市场是保护国家免遭恐怖袭击的唯一方式或最佳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决定忍受这种期货市场所会助长的那种低劣的道德感了。但是,那将会是一种吃大亏的交易,而且对它保持厌恶感也仍是至关重要的。
当死亡市场为人熟知并变成一种惯例的时候,对它的那种道德轻蔑也就不易再保有了。在一个人寿保险正在变成(正如18世纪的英国)一种投机工具的时代,牢记上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赌的行为,已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赌局游戏,而是一项支柱产业了。
延长生命的艾滋病药物是健康的福音,但却是保单贴现行业的诅咒。投资者们发现自己被套住了,因为他们要为那些无法按预期那样快速“到期”的人寿保险支付保险费。如果这门生意要想存续下去的话,那么保单贴现经纪人就需要找到更为可靠的死亡去投资。在研究了癌症患者和其他绝症患者之后,他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要把这项生意局限在患者身上呢?为什么不从那些愿意需要现金的健康老年人那里购买人寿保险单呢?
艾伦·伯格(Alan Buerger)是这一新兴产业的开拓者。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向公司出售普通员工保险。当国会削减了普通员工保险的税收好处时,伯格曾考虑转入保单贴现行业。但是,他当时冒出了一个想法,即健康富裕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更大且更有前景的市场。伯格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我当时觉得豁然开朗。” [52]
2000年,他开始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那里购买人寿保险单,并把它们倒卖给投资者。这种生意的运作与保单贴现生意一样,只是在这种生意中人的寿命预期更长,而且保单的价值一般也更高,常常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投资者从那些不再需要这些保单的人那里将其买下并支付保险费,然后在这些人去世以后收取死亡保险金。为了避免染上与保单贴现相关联的那种污名,这门新生意把自己称作“寿险保单贴现”(life settlement)产业。伯格的公司,即考文垂第一公司(Coventry First),乃是这个行业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53]
寿险保单贴现产业以“人寿保险自由市场”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此之前,那些不再想要或不再需要其人寿保险单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让这些保单失效,或者在某些情形中只能向保险公司折兑现金以求拿到很少一点退保金。而现在,他们则可以通过把他们不需要的保单抛售给投资者而从中获得更多好处。 [54]
无论从哪方面听上去这都像是桩好买卖。老年人可以把他们不需要的人寿保险单卖个公道的价钱,而投资者则在这些保单到期时获得保险金。但是,这种人寿保险的二手市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大量诉讼。
一种争议是由保险业的经济核算而引起的。保险公司不喜欢寿险保单贴现。在确定保险费的时候,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假定,有一定数量的人会在他们去世之前放弃他们的保单。一旦孩子们长大成人而且配偶也得到了供养,那些保单持有人便常常会停止支付保险费并使保单自动失效。事实上,几乎有40%的人寿保险单最终保险公司都没有偿付死亡保险金。但是,随着更多的保单持有人将他们的保单卖给投资者,失效的保单更少了,而且保险公司将不得不偿付更多的死亡保险金(也就是说,偿付给那些一直支付保险费并最终获赔的投资者们)。 [55]
另一种争议涉及拿生命作赌注的道德窘境。对于寿险保单贴现来说,与保单贴现一样,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被投保人何时死亡。2010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生命伴侣控股公司(Life Partners Holdings)的情况。这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寿险保单贴现公司,它曾经低估了那些将保单卖给投资者的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例如,这家公司将爱达荷州一名79岁牧场主的一份价值200万美元的人寿保单卖给了投资者,断言他只有2~4年的寿命。但是5年多过去了,这位在当时已经84岁的牧场主依然身体强健,能在跑步机上跑步、举重和伐木。他说:“我壮得像头牛,很多投资者都要大失所望了。” [56]
《华尔街日报》发现,这位健康的牧场主并不是唯一令人失望的投资。在生命伴侣控股公司作为经纪人所办理的95%的保单中,被投保人在该公司之前预测的预期寿命到了以后依然生龙活虎。这些过于乐观的死亡预测,是由内华达州里诺市一名受雇于该公司的医生做出的。《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这家公司就因其不靠谱的寿命预测而受到了得克萨斯州证券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57]
得克萨斯州的另一家寿险保单贴现公司也由于在预期寿命上误导了投资者而在2010年被该州关闭了。沃思堡市一名退休的执法官员莎伦·布雷迪(Sharon Brady)曾经被告知,通过对陌生老年人的生命进行投资,她可以获得16%的年度回报。布雷迪说:“他们拿出一本书并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人的照片和年龄,而且还有一位医生向我们解释了他们每个人都患有什么样的疾病以及预计他们还能活多久。你不应当希望某人死亡,但是如果他们死了,你就可以赚钱。因此,你真的是在拿他们何时死掉来赌博。”
布雷迪说她“对此感到有点奇怪。你居然可以从你投入的这笔钱中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议,但却是一个具有经济吸引力的提议。她和她的丈夫投资了5万美元,只是后来才得知这些寿命估算只是说得好听,但却错得离谱。“很显然,那些人活得比那个医生告诉我们的要久一倍。” [58]
这种生意还存在另一个争议,而这涉及它筹措可售保单的独创方式。到2005年左右,人寿保险二手市场已经成了一个行业。像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这样的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都花费了数十亿资金去购买老年富人的人寿保险单。随着人们对这种保单的需求的增长,一些经纪人开始付钱给那些没有投保的老年人,让他们去办理大额人寿保单并随后将这些保单转售给投机者。这些保单被叫作“投机者始购保单”(speculator-initiated policies)或“人寿转手保单”(spin-life policies)。 [59]
2006年,据《纽约时报》估计,这个人寿转手保单市场一年的金额接近130亿美元。该报对那种招揽新生意的狂热做了如下描述:“这些交易如此划算,以至于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巴结那些老年人。在佛罗里达州,投资者还为那些愿意在游轮上接受体检并申请人寿保险的老年人安排了免费的航游。” [60]
在明尼苏达州,一位82岁的男子从7家不同的公司购买了价值1.2亿美元的人寿保险,然后将这些保单以一笔可观的利润卖给了投机者。这些保险公司大呼违规并抱怨说:第一,以纯粹投机的方式利用人寿保险的做法,不符合其保护家庭成员免遭经济灾难的基本目的;第二,人寿转手保单会抬高合法客户购买人寿保险的成本。 [61]
一些人寿转手保单最终被告上了法庭。在一些案件中,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死亡保险金,声称这些投机者不具有可保权益。而寿险保单贴现公司一方却论辩说,许多包括企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在内的投保人,都欢迎人寿转手保险业务及其高昂的保险费,只是在赔付的时候才会抱怨。其他一些则是被经纪人招募来购买人寿保险以转售给投机者的老年客户状告这些经纪人的诉讼。 [62]
一位不幸的人寿转手保单客户,是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他为自己买了两份总面值为1 5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并立即卖掉了它们。尽管金已经为他的这个麻烦支付了140万美元,但是他却在一起诉讼中声称,经纪人在佣金、费用和税收信息等方面误导了他。金还控告说,他无法查明现在是谁对他的死亡拥有经济利益。他的律师说:“我们不知道这位保单所有者是华尔街的一家对冲基金,还是一名黑手党教父。” [63]
保险公司与寿险保单贴现业之间的官司还打到了美国各州的立法机关。2007年,高盛集团、瑞士信贷银行、瑞士银行、贝尔斯登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成立了“人寿市场制度协会”(Institutional Life Markets Association)以促进寿险保单贴现业的发展,并就反对各种限制它的努力展开游说。这家协会的任务是:为“与寿命和死亡相关的市场”设计“各种创新性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 [64] 这就是死亡赌博市场的一种礼貌说法。
到2009年,大多数州已经颁布法律禁止人寿转手保单或一如它最终被称为的“源自陌生人的人寿保险”(stranger-originated life insurance, 简称STOLI)。但是,这些法律却允许经纪人继续从事关于患者或老年人的人寿保险单交易——他们是自己购买保单的,而不是受投机者怂恿购买保单的。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的管制,寿险保单贴现业力图把它所支持的“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stranger-owned life insurance)与它现在所反对的“源自陌生人的人寿保险”做出原则性的区别。 [65]
从道德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投机者引诱老年人为了迅速获利而购买并转售人寿保险单的做法,看起来确实是极其低俗的。这种做法肯定不符合那种给予人寿保险以正当性证明的目的——保护家庭和企业免遭因养家之人或主要行政主管去世而导致的经济灾难。但是,所有的寿险保单贴现方案都具有这种低俗性。不论这种保单源自谁,任何拿别人的生命进行投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一位寿险保单贴现业的发言人道格·黑德(Doug Head)在佛罗里达州一次保险听证会上作证时论辩说,让人们把他们的人寿保险单卖给投机者的做法“维护了财产权,并代表了竞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一旦一个拥有合法可保权益的人购买了一份保单,他/她就应当可以自由地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是保单所有人在开放市场中出售其保单的基本财产权的自然结果。”黑德坚持认为,源自陌生人的保单与“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不尽相同。这种保单之所以是非法的,乃是因为那些最初购买这种保单的投机者并不具有可保权益。 [66]
这种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最终拥有保单的投机者,都不具有针对那位老年人(其死亡会导致保险金赔付)的可保权益。此外,上述两种情形都创制了一种与陌生人早死相关的经济利益。正如黑德所声称的,如果我有基本权利购买和出售自己的人寿保险的话,那么我行使这项权利是出于我自己的动机还是听从了他人的建议,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寿险保单贴现的优点在于它们“开启了”我已经拥有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那么人寿转手保单的优点就在于它们开启了我垂暮之年的现金价值。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某个陌生人都从我的死亡中获利了,而且我也得到了一些钱可以安然离开了。
日益发展的死亡赌博市场只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在华尔街上市。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计划收购寿险保单贴现业,把它们打包成债券,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资者。这些债券会从保险赔付中产生一条收益流(income stream),而这些赔付会在原始保单持有人死亡时予以支付。华尔街会用它在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住房抵押的做法来处理死亡赌博问题。 [67]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高盛集团已经开发了一种寿险保单贴现的可交易指数,从而使投资者可以就人们是否会比预期活得长或比计划死得早进行赌博”。而且瑞士信贷银行也在创制“一条购买大量人寿保险单、对其进行打包和转售的金融流水线——正如华尔街的公司对次级证券所做的那样”。鉴于美国有26万亿美元的人寿保险单,而且寿险保单贴现交易也在不断发展,因此死亡市场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希望,这种产品可以弥补由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崩溃而导致的利益损失。 [68]
尽管一些商业信用等级评定机构还有待说服,但至少人们相信,创造一种风险最低、以寿险贴现为根据的债券是有可能的。正如抵押贷款证券从全国各地收集贷款一样,寿险贴现所支撑的债券也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些人那里收集到保单,他们“患有各种疾病,如白血病、肺癌、心脏病、乳腺癌、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等”。一种以多种疾病组合为支撑的债券,可以使投资者高枕无忧,因为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案的发现,都不会使这种债券的价格跌落谷底。 [69]
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复杂的金融交易方案曾推动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这家公司也对这种债券产生了兴趣。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它曾经反对寿险贴现业并在法庭上与他们唇枪舌剑。但是它却悄悄地买断了目前市场上450亿美元寿险保单中的180亿美元,而且现在还希望把它们打包成证券并作为债券进行出售。 [70]
那么,死亡债券的道德地位又是什么呢?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它们比作作为其基础的死亡赌博。如果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反对拿他人的生命进行赌博并从他人的死亡中获利的行为,那么死亡债券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种做法(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死亡赌局以及人寿保险中各种纯粹的投机交易)一样都存在这种缺陷。人们有可能会论辩说,死亡债券的匿名性质和抽象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它对我们的道德感的腐蚀性影响。一旦人寿保单被大规模地打包收购,然后再被切割分散并抛售给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那么任何投资者就不会与任何特定的人的死亡保有一种紧密利益了。不可否认,如果国家健康卫生政策、环境标准或得到改善的饮食与锻炼习惯,使人们变得更加健康和长寿的话,那么死亡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但是,与计算那位患艾滋病的纽约人或爱达荷州牧场主死亡的日期相比较,一个人打赌死亡债券的价格不可能下降这件事,麻烦似乎总是要少一些。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种道德败坏的市场做法提供了社会之善而决定容忍它。人寿保险最初就是人们做出的这样一种妥协。为了保护家庭和企业免遭养家之人或企业主管过早死亡而产生的经济风险,各国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勉强得出结论:应当允许那些对某人的生命拥有可保权益的人对死亡进行押注。然而,事实证明,投机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
正如今天大规模的生命与死亡市场所证实的那样,使保险摆脱赌博名声的艰苦努力还没有大功告成。由于华尔街积极推进死亡债券交易,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伦敦劳埃德咖啡馆那个无拘无束的道德世界中,只不过它现在的规模,使得人们就陌生人的死亡与不幸所押的赌注,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有点离奇了。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长大,还是个棒球发烧友。那时候,我所支持的明尼苏达双城队(Minnesota Twins)在大都会体育场打主场比赛。1965年,那时我12岁,运动场中性价比最高的座位要花3美元,露天看台的座位要花1.5美元。那一年,明尼苏达双城队参加了职业棒球联赛,而我至今仍然保留着我和父亲一起去看的第7场比赛的票根。我们坐在本垒和第三垒间的第三层看台上。票价是8美元。在那场比赛中,伟大的道奇队投手桑迪·柯法斯(Sandy Koufax)打败了明尼苏达双城队,并为道奇队奠定了冠军地位,为此我的心都要碎了。
在那些年里,明尼苏达双城队的明星球员是哈蒙·基利布鲁(Harmon Killebrew);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本垒打球员之一,现在是棒球名人堂中的一员。在哈蒙·基利布鲁职业生涯的顶峰,他一年能挣12万美元。那些日子,球员是没有转会自由的,因为球队控制了球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权利。这意味着球员几乎没有能力就薪水问题与球队进行谈判。他们要么必须为他们所在的球队打球,要么就根本没球打。(这一体制在1975年被废除。) [1]
自那时起,棒球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为明尼苏达双城队效力的明星球员乔·莫尔(Joe Mauer),最近刚签了一份为期8年价值1.84亿美元的合同。莫尔每年能挣2 300万美元,他每一场比赛(实际上是17局比赛)所挣的钱比基利布鲁整个赛季挣的钱还要多。 [2]
不必惊讶,棒球比赛的票价也飞涨了。现在,观看明尼苏达双城队比赛一个包厢座位的价格是72美元,而且运动场中最便宜座位的价格也要11美元。再者,明尼苏达双城队的票价还算是比较便宜的。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比赛的一个包厢座位要260美元,而露天看台上一个角度不好的座位的价格也要12美元。我小的时候没听说过棒球场上有企业包厢和豪华包厢,它们更贵,当然也为球队带来了大笔收入。 [3]
棒球比赛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我在这里所考虑的并不是指定击球员(the designated hitter),即人们激烈争论的美国棒球联盟中免去投手击球这项规则的变化。我所考虑的乃是棒球中各种反映了市场、商业主义以及经济思想在当代社会生活里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变化。自职业棒球赛在19世纪晚期诞生以来,它一直是一项生意,至少在部分上是如此。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那个年代狂热的市场环境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娱乐活动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下面让我们考虑一下比赛纪念品交易的问题。长期以来,棒球运动员一直是嚷嚷着索要亲笔签名的年轻球迷们狂热追逐的目标。在赛前或者有时候在赛后离开体育场时,比较礼貌的运动员会在球员休息处附近为球迷在记分卡和棒球上签名。今天,原本单纯亲笔签名的热闹场面已然被10亿美元计的纪念品交易取代了,而经纪人、批发商以及球队自身则支配着这种交易。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亲笔签名之旅是在1968年,那年我15岁。在此之前,我家已经从明尼阿波利斯搬到了洛杉矶。那年冬天,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拉科斯塔(La Costa)举办的一场慈善高尔夫比赛的外场区闲逛。一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棒球员在那场比赛中出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球洞与球洞之间的地方为球迷亲笔签名。我事先并没想到要带棒球和永久马克笔。我身上只有一张5寸长、3寸宽的空白卡片。一些球员用墨水笔签名,另一些则拿他们用来记高尔夫成绩的小铅笔签名。但是我得到了珍贵的亲笔签名,并激动地遇见了(尽管时间短暂)我年轻时代的英雄和在这之前就参加比赛的一些传奇人物:桑迪·柯法斯、威利·梅斯(Willie Mays)、米基·曼特尔(Mickey Mantle)、乔·迪马乔(Joe DiMaggio)、鲍勃·费勒(Bob Feller)、杰基·鲁宾逊(Jackie Robinson),居然还有哈蒙·基利布鲁。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出售这些亲笔签名,甚或也从不想知道它们在市场上会卖什么价钱。我至今仍珍藏着它们,当然还有我的棒球卡收藏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把体育界名人的亲笔签名和随身用品看作是可买卖的物品,而且买卖它们的收藏家、经纪人和经销商也越来越多。 [4]
棒球明星开始收费签名,而所收的费用也因他们地位的不同而不同。1986年,名人堂投手鲍勃·费勒在收藏家展览会上以每个2美元的价格出售他的亲笔签名。3年后,乔·迪马乔签一次名的价格是20美元,威利·梅斯的是10~12美元,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的是15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费勒的签名价上升到了10美元。)由于这些已经退役的棒球大腕是在高薪时代到来之前就打球的,所以很难责怪他们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大捞一笔。但是现役运动员也加入了巡回签名的队伍中。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在那时是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的一位明星投手,他每一次亲笔签名的价格是8.5美元。包括道奇队投手奥雷尔·赫希泽(Orel Hershiser)在内的一些运动员认为,这种做法是令人反感的。棒球传统捍卫者对这种付费签名的做法表示哀叹,因为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贝比·鲁斯(Babe Ruth)当年总是免费为人签名的场景。 [5]
然而,纪念品市场在当时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1990年,《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发表了一篇描述索要亲笔签名这一长期存在的做法是如何转变的文章。“亲笔签名的新型收藏者不仅粗鲁,而且冷酷,他们的动机就是钱”,他们在旅馆、饭店甚至运动员的家里不断地纠缠明星。“索要亲笔签名的人在过去只是那些崇拜其心目中的英雄的孩子,而现在索要签名的人还包括收藏者、经销商和投资者……这些经销商常常同一些他们付钱雇来的孩子一起干这个事。这有点类似于费金与他的机灵道奇队(Artful Dodgers)的关系。他们收集明星的亲笔签名,然后转身就卖掉这些签名。投资者购买明星的亲笔签名,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如同收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艺术品或人工制品一样,比如,伯德、乔丹、马丁利或者乔斯·坎塞科(Jose Canseco)的签名,它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值。” [6]
20世纪90年代,经纪人开始付钱给棒球运动员,让他们在成千上万的球、球棒、运动衫以及其他物品上签名。然后经销商通过商品目录公司、有线电视频道和零售店售卖这类大规模生产的纪念品。1992年,米基·曼特尔通过给2万个棒球签名和收取个人出场费,据说他挣了275万美元,比他在扬基队的整个运动生涯挣的还多。 [7]
然而,最大的价值则表现在运动员在比赛中所使用的那些物品上。1998年,当马克·麦圭尔(Mark McGwire)创造了一个对大多数赛季本垒打来说的新纪录时,人们对纪念品的追逐变得更疯狂了。拿到麦圭尔创下纪录的第70个本垒打的球的那个球迷,在一场拍卖会上把它卖了300万美元,使得这个球成为有出售记录以来最为昂贵的一件比赛纪念品。 [8]
棒球纪念品向商品的转变,改变了球迷与比赛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当麦圭尔在那个赛季击中他的第62个本垒打(这个球破了以前的纪录)时,找回这个球的蒂姆·福尔内里斯(Tim Forneris)没有把它卖掉,而是即刻还给了麦圭尔。他递上球说:“麦圭尔先生,我想我手上拿的是属于你的东西。” [9]
考虑到这个球的市场价值,蒂姆·福尔内里斯的这种慷慨行为引发了一连串的评论——大多数是赞扬的,也有些是批评的。这个22岁的兼职球场管理员受邀去迪士尼世界游玩,应邀参加戴维·莱特曼的脱口秀节目,并被邀请到白宫会见克林顿总统。他还去小学给孩子们演讲,告诉他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尽管福尔内里斯受到众多的赞扬,然而《时代》杂志的一位个人理财专栏作家却还是对他的轻率行为进行了责难,他把福尔内里斯归还那个球的决定说成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犯的几个个人理财错误”的一个例子。这位专栏作家还说,只要他“用棒球手套接住了这个球,那么这个球就是他的了”。把球还给麦圭尔这个举动,例证了“一种致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理财事务中犯严重错误的既定心态”。 [10]
这里还有一个说明市场如何改变规范的例子。一旦一个创纪录的棒球被看作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那么把球还给击打它的运动员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体面姿态了。它要么是一种英雄般的慷慨行为,要么是一种愚蠢的挥霍行为。
3年后,巴里·邦兹(Barry Bonds)在一个赛季中击出了73个本垒打,打破了麦圭尔的纪录。人们为了抢到这个球而大打出手,这不仅成了看台上的丑陋一幕,而且也导致了一场漫长的法律诉讼纠纷。接到这个球的球迷被一群试图抢夺这个球的人打倒在地。这个球滑出了他的手套,并被站在附近的另一个球迷捡到了。他们两个人都主张这个球从道理上讲是自己的。这场诉讼引发了几个月的法律争论,并最终由法院进行审判。这场审判由6位律师和数名由法院指定的法学教授组成的陪审团参加——法院要求这个陪审团就什么因素构成拥有一个棒球的问题做出界定。法官最后裁定说,这两位权利主张者应当卖掉这个球并分享收益。结果,这个球卖了45万美元。 [11]
现在,纪念品的市场营销已成为棒球比赛的一个常规部分。甚至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的残留物,如运动员用过的破球棒和球,也都被卖给了那些热心的买家。为了向收藏家和投资者保证比赛所用设备的真实性,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每一场比赛现在至少有一名官方“认证者”值班。这些认证者装备有高科技的全息图贴纸,它们会记录并验证销往价值几十亿美元纪念品市场的棒球、球棒、垒、运动衫、排卡和运动员其他随身用品的真实性。 [12]
2011年,德里克·杰特(Derek Jeter)的第3 000次击打是纪念品产业的一件幸事。在与一个收藏者的一笔交易中,这位著名的扬基队游击手在他里程碑式的一击后的第二天,在1000个纪念性棒球、照片和球棒上签了名。这些亲笔签名的棒球卖到了699.99美元,球棒卖到了1099.99美元。他们甚至出售他走过的土地上的泥土。在杰特完成第3 000次击打的比赛后,一个球场管理员从杰特站过的击球手击球区和游击位置那里收集了5加仑的泥土。装有神圣泥土的桶被封存起来并贴上了认证者的全息图,后来这桶泥土被一匙一匙地卖给了球迷和收藏者。当扬基队的老体育场被拆除的时候,人们也把泥土收集起来并拿去出售。一个纪念品公司声称自己卖掉了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真正的扬基队体育场的泥土。 [13]
一些球员还试图利用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做法来赚钱。最棒的击球领袖彼得·罗斯(Pete Rose)因为赌球而被开除出棒球界。他有一个网站,专门用来出售与他被开除的事件有关的纪念品。花299美元,另加运费和手续费,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由他亲笔签名并刻有“我为自己赌球道歉”字样的棒球。花500美元,你就会收到一份上面有他亲笔签名的把他从棒球界开除的文件复制本。 [14]
其他的球员试图出售一些更加怪异的物品。2002年,亚利桑那响尾蛇队(Arizona Diamondbacks)的外场手路易斯·冈萨雷斯(Luis Gonzalez)据说为了慈善事业,在网上要价1万美元拍卖一块他嚼过的口香糖。西雅图水手队(Seattle Mariners)的投手杰夫·纳尔逊(Jeff Nelson)在做完肘部手术后,把他肘部的那些骨头片放在eBay上进行出售。在eBay上根据一项反对出售人体器官的规则终止这项拍卖之前,竞价居然达到了23 600美元。(有关公告并没有说明在他进行这项手术时认证人员是否在场。) [15]
运动员的亲笔签名和随身物品并不是拿来买卖的所有东西。棒球场的名称也可以买卖。尽管一些体育场仍然沿用它们的历史名称,比如,扬基体育场、芬威公园,但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大多数棒球队现在却都在向最高出价者出售体育场的冠名权(naming rights)。银行、能源公司、航空公司、科技公司以及其他企业都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赢得人们的关注,而其方式便是用它们的名称来冠名大联盟各个球队的棒球场和活动区域。 [16]
芝加哥白袜队(Chicago White Sox)在科米斯基公园(Comiskey Park)进行了81年的比赛,而这个运动场乃是以该队早期一位老板的名字命名的。现在,这个球队在一个叫“美国移动通讯球场”(U.S. Cellular Field)的宽敞体育场打球,而该体育场就是由一个移动通讯公司冠名的。圣迭戈教士队(The San Diego Padres)在佩特科公园(Petco Park)打球,而该体育场则是由一个宠物供应公司冠名的。我所喜欢的那个老球队明尼苏达双城队现在在标靶球场(Target Field)打球,而这个球场得到了一家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零售业巨头的赞助;此外,这家公司还把它的名字放在了附近的明尼苏达森林狼队(Minnesota Timberwolves)进行篮球比赛的球场(即标靶中心)上。在体育界最昂贵之一的一项冠名权交易中,一家金融服务公司(花旗集团)在2006年下半年同意出资4亿美元获得20年冠名纽约大都会队(New York Mets)新棒球场即“花旗球场”的权利。到了2009年,即大都会队在该体育场打第一场比赛的那年,金融危机给这项赞助安排留下了阴影;批评者们抱怨说,这项安排现在是由花旗集团的纳税人紧急援助予以资助的。 [17]
橄榄球体育场也是吸引企业赞助者的地方。新英格兰爱国者队(The New England Patriots)在吉列体育场(Gillette Stadium)比赛,而华盛顿红皮队(Washington Redskins)则在联邦快递球场(FedEx Field)比赛。梅赛德斯–奔驰公司(Mercedes-Benz)最近购买了新奥尔良的超级碗,即圣徒队大本营的冠名权。截止到2011年,全美美式橄榄球大联盟的32支球队中有22支在企业赞助者冠名的体育场中进行比赛。 [18]
由于出售体育场的冠名权在今天已经极为常见,所以人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做法乃是在最近才流行开来的。这种做法与棒球运动员开始出售他们的亲笔签名大致是同时出现的。1988年,只有3个体育场进行了冠名权交易,总价值仅有2500万美元。到2004年,已经达成了66项交易(这个数字要比职业棒球、橄榄球、篮球和曲棍球比赛的所有体育馆和体育场的一半还多),总价值达36亿美元。到2010年,在美国,已经有超过100家公司花钱给大联盟的体育场或体育馆冠名。2011年,万事达信用卡公司购买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篮球馆的冠名权。 [19]
企业的冠名权不只是在体育场的大门上打个标记,它们还延伸到了广播员在描述比赛动作时的用语。当一家银行购买了亚利桑那响尾蛇队体育场(第一银行棒球场)的冠名权时,这项交易还要求该队的广播员把每一个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本垒打都称作“第一银行本垒打”。大多数球队还没有公司赞助的本垒打。但是一些球队已经出售了投球变化的冠名权。当球队经理走上投球区土墩召唤一个新投手时,某些广播员按照合同约定,必须称这一举动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呼叫候补投手区(即新投手上场前的暖身区)”。 [20]
甚至滑进本垒现在也成了企业赞助的事情。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10支棒球队达成了一笔交易,而这笔交易要求在一个运动员每次成功滑垒时做一次推销宣传。所以,比如,当裁判员判定一个跑垒者安全抵达本垒板时,一家企业的标识就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专事报道的广播员也必须说:“安全抵达本垒。既安全又保险。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这并不是两局比赛之间出现的商业广告用语,而是企业赞助播报比赛本身的一种方式。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裁和广告主管解释说:“这句广告语很自然地融入了棒球比赛之中。”它“对那些为他们最喜爱的球员安全达垒而欢呼的球迷来说是个重要的提示,即同美国最大的互助人寿保险公司在一起,他们也可以是既安全又保险的。” [21]
2011年,黑格斯城太阳队(马里兰的一支小俱乐部联盟棒球队)得到了棒球比赛中最后一块未开发领域的商业赞助:他们向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出售了一个运动员上场击球的冠名权。每当该队最佳击球手和极有望进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打球的运动员布赖斯·哈珀(Bryce Harper)上场击球时,该队就会广播说:“现在上场击球的是米斯公用事业公司(Miss Utility)推荐给你们的布赖斯·哈珀。请在你进行挖掘作业之前,不要忘了拨打电话811。”这一不搭调的商业广告信息是什么意思呢?显而易见,这家公司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影响那些正在从事有可能损毁地下公用事业线路的建筑事务的棒球球迷。该公用事业公司的市场主管解释说:“在布赖斯·哈珀采用棒头着地击球法之前对球迷们进行这样的宣讲,是提醒在场所有球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知道在进行每一次挖掘作业之前联系米斯公用事业公司的重要性。” [22]
到目前为止,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还没有一支球队出售过运动员的冠名权。但是在2004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确实进行过出售垒板广告的尝试。在一项同哥伦比亚图片公司(Columbia Pictures)的广告推广交易中,棒球官方同意在7月份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每个棒球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垒上放置3天即将上映的电影《蜘蛛侠2》(Spider-Man 2)的广告标识。本垒板上依旧不放任何广告。然而,事后引发的公众反对浪潮,最终使得这一新的广告举措被迫取消。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已然充满浓重商业味的棒球比赛中,垒依旧是神圣的。 [23]
像美国人生活中少数其他制度一样,棒球、橄榄球、篮球和曲棍球乃是社会凝聚和公民自豪的一个源泉。从纽约的扬基体育场到旧金山的烛台公园(Candlestick Park),体育场都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大教堂,即以失败与希望、亵渎与祈祷的仪式把各色人等聚集到一起的公共空间。 [24]
然而,职业运动不仅是公民认同的一个源泉,也是一种商业。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运动中的金钱因素也一直在排挤共同体因素。那种认为冠名权和企业赞助毁掉了主队之根基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改变一个城市地标的名称却会改变它的意义。这便是底特律的球迷们在老虎体育场(底特律橄榄球队也以此为名)更名为一家银行的名号“科莫利卡公园”(Comerica Park)时深感悲痛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丹佛野马队(Denver Broncos)的球迷们在发生下述事情时甚感恼怒的原因,即他们挚爱的让人产生无限空间感的“英里高体育场”(Mile High Stadium)被一个让人想到一家互惠保险公司的“银威斯科球场”(Invesco Field)所取代了。 [25]
当然,体育场主要是人们聚在一起观看体育比赛的地方。当球迷去棒球场或体育场时,他们主要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公民体验。他们是去看戴维·奥尔提斯(David Ortiz)在第9局的最后时刻打出一个本垒打,或是去看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在一场橄榄球比赛的最后几秒钟触地得分。但是,这种场景的公共性质仍然透露出了一种公民教育因素: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也就是说至少有几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分享一种空间感和公民自豪感。当体育场更少像地标而更多像广告场时,它们的公共性也就变弱了。也许,它们所能激发的那种社会凝聚力和公民感也在变弱。
伴随公司冠名权的兴起而出现的大量设置豪华包厢的趋势,更强烈地侵蚀了运动中教育公民的因素。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去看明尼苏达双城队比赛时,最贵的座位和最便宜的座位之间的差价只有2美元。实际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司高管和蓝领工人在棒球场上都坐在一起观看比赛,每个人都要排队买热狗或啤酒,而如果下雨的话,富人和穷人一样都会被淋湿。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赛场上方高耸的包厢套间的出现,把富人和特权者同下面看台上的普通民众隔开了。
尽管超前的休斯敦太空人体育场(Houston Astrodome)于1965年最早设置了豪华包厢,但只是当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于20世纪70年代在得克萨斯体育场(Texas Stadium)设置豪华套房时,包厢才开始真正流行起来。企业花成千上万美元在位于平民百姓座位上方的豪华包厢里招待公司高管和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至少有12支球队跟随牛仔队的脚步,在高空玻璃房中极其热情地款待那些富有的球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会虽说削减了企业因支付包厢费而声称的税收减免额度,但是这并没有遏制人们对免受风吹雨淋的包厢的需求。
从豪华包厢中赚到的收入对于球队来说是一笔横财,并且推动了体育场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但是评论者却抱怨说,摩天豪华包厢毁掉了体育运动所具有的阶级调和这一功用。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n)写道:“摩天豪华包厢完全因为其舒适的轻薄而证明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根本缺陷:精英们急切地甚至拼命地要把他们自己从其余的大众中分离出去……职业运动比赛曾经是舒缓身份焦虑的一剂良药,但是现在却被这种病毒严重侵害了。” 为《新闻周刊》(Newsweek)写作的一位作家弗兰克·德福特(Frank Deford)指出,大众体育运动最迷人的地方永远是它“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性……体育场有助于盛大的公共集会,就像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的一片20世纪的社区绿地”。但是最近出现的豪华包厢“却把有身份的人同广大民众完全隔离开来;对此,我们可以公平地说,美国体育运动赛场座位的豪华程度,可以使其夸耀地说自己是娱乐圈中阶层分化最明确的地方”。得克萨斯州一家报纸把摩天豪华包厢称作“运动版的封闭住宅区”,它能使富裕的包厢享用者“把他们自己同其余的公众隔离开来”。 [26]
尽管体育场的摩天豪华包厢招致了很多抱怨,但是它们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职业体育场以及很多大学体育馆的一个标志性设施。虽说包括豪华包厢和俱乐部座席在内的贵宾席只占了体育场所有座位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们几乎却占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一些球队门票收入的40%。2009年开始投入使用的新扬基体育场比旧体育场少了3 000个座位,但是豪华包厢却比原来多了两倍。很多人都等着购买波士顿红袜队在芬威公园的40个豪华包厢的套票,而这些赛季套票的价格要高达35万美元。 [27]
一些设立了一流运动项目的大学,也感到摩天豪华包厢的收入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截止到1996年,美国近36个大学体育场设置了豪华包厢。到2011年,除了诺特丹大学(Notre Dame)以外,美国大学橄榄球联盟中几乎每所大学的体育场都开设了豪华包厢。联邦税法也给予那些使用大学体育场摩天豪华包厢的人以一项特别的税收政策,即允许豪华包厢套票的购买者从购票费用中扣除80%的费用作为对该大学的慈善捐助。 [28]
最近一次关于摩天豪华包厢道德论战发生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它是美国最大的大学体育场所在地。众所周知,密歇根大学体育场是“大宅子”;自1975年以来,密歇根大学体育场的每一场主场橄榄球比赛都吸引了10万多名球迷。2007年,当该大学的校董们考虑一项用2.26亿美元翻新体育场的计划(包括为这个具有标准传统风格的体育场增建摩天豪华包厢)时,一些校友提出了抗议。一位校友论辩说:“对于大学橄榄球,尤其是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来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是汽车工人和富豪可以在一起为他们的球队呐喊喝彩的地方。” [29]
一个被称作“拯救大宅子”的群体着手收集请愿书,希望说服校董们拒绝增建豪华包厢的计划。评论者写道,在过去的125 年中,“富人和普通民众一直不分彼此地站在一起,在一起紧张、在一起喝彩,并在一起赢得胜利。私人豪华包厢所代表的正是那种传统的对立面,因为它们根据收入多少把密歇根的球迷分成了两部分,而且还伤害了各种年龄和不同背景的密歇根球迷原来在一起观看比赛时所共享的那种团结、兴奋和友情。那种试图在密歇根体育场增建私人豪华包厢的想法,乃是与密歇根大学所致力于的那些平等理想相悖的。” [30]
最后,人们的抗议还是失败了。校董会后来以5:3的票决通过了为密歇根体育场增建81个豪华包厢的计划。当修缮一新的体育场于2010年投入使用时,一间可供16人享用的豪华包厢的价格上涨到每个赛季85 000美元,其中包括停车费。 [31]
纪念品市场、冠名权和摩天豪华包厢在最近几十年的兴起,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受市场驱动的社会。市场逻辑在体育界中的另一个例子,乃是最近人们把棒球变成“金钱”的事例。“点球成金”这个术语是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其2003年出版的一部畅销书中提出来的,而且他还用金融界的洞见分析了一个棒球故事。在《点球成金:逆境中制胜的智慧》(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一书中,刘易斯描述了一个支付不起昂贵球星薪水的小市场球队(奥克兰运动家队)是如何设法赢得与富有的纽约扬基队一样多的比赛场次,尽管它只有后者1/3的薪水总额。
当时,在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领导下,奥克兰运动家队用廉价的方式打造了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而其关键便在于:第一,运用统计分析去辨识那些技术被人低估的球员;第二,采用与传统棒球智慧不同的策略。比如,他们发现,对于赢球来说,高上垒率比高打击率或长打率更重要。于是,他们雇用了一些能够打出很多保送上垒球的球员,虽说这些球员没有高价的长打球员那么出名。传统的棒球观点认为,偷垒可以赢得比赛,但是他们却发现,偷垒的尝试在一般意义上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球队得分的机会。于是,他们甚至不鼓励他们速度最快的运动员去尝试偷垒。
比恩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至少一度是如此。2002年,当刘易斯跟踪运动家队进行分析的时候,该队赢得了美国联盟的西部冠军。尽管奥克兰运动家队在季后赛中被打败,但是它的复杂历程却是一个吸引人的“戴维和巨人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传说:一个缺乏资金的小球队运用其智慧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与一个像扬基队这样富有且强大的球队进行竞争。在刘易斯的描述中,奥克兰运动家队也是精明的投资者如何充分利用市场缺陷而获益的一个实例。比恩把新型量化分析商人(quantitative traders)带给华尔街的东西运用到了棒球比赛之中,而这就是那种运用计算机分析战胜那些依赖直觉和个人经验的老前辈的能力。 [32]
2011年,人们把《点球成金》拍成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布拉德·皮特饰演比利·比恩这一角色。这部电影令我很扫兴。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布拉德·皮特一如既往地迷人、有魅力。那么为什么这部电影如此令人感到不满呢?部分是由于它忽视了这个队的球星——3个卓越的年轻首发投手和全明星游击手米格尔·特哈达(Miguel Tejada),反而把重点放在了比恩因为那些有能力打出保送上垒球而与他们签约的边缘球员身上。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很难为计量分析方法和较有效的价格机制的胜利喝彩。量化分析方法和较有效的价格机制,而非运动员,才是《点球成金》的真正主角。 [33]
实际上,我确实知道,至少有一个人认为价格功效是鼓舞人心的。而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拉里·萨默斯(就是那位我在前文讨论过的在晨祷演讲中主张节约使用利他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在2004年作为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把《点球成金》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过去30年或40年中所发生的一场重要的知识革命”:这就是作为“一种科学真实形式”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兴起。他解释了“一个极具智慧的棒球总经理是如何通过雇用一位计量经济学博士”计算出能够帮助球队取胜的棒球技巧和策略的。萨默斯在比恩的成功中还窥见了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棒球的点球成金法可以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提供各种教益。“棒球在这个方面的成功之道,实际上也可以适用于更为广泛的人类活动。”
在萨默斯看来,这种科学方法(即点球成金法)的智慧还会在其他什么领域胜出呢?在环境监管领域,“坚定的环保活动家和律师”将让位于“熟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人”。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现在更需要的是“那些聪明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硕士”,而不是那些在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聪明的年轻律师。在华尔街,掌握电脑专业技能的计量分析专家正在取代那些专事闲谈的健谈者,并且正在发明各种新型的复杂衍生品。萨默斯说:“在过去的30年中,投资银行这个领域已经为那些擅长解决定价衍生债券中高难度数学问题的人所控制,而不再为那些擅长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酒吧间会见客户的那些人所把持。” [34]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4年前,市场必胜论的信念(点球成金的信念)已经明显展现出来了。
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市场必胜论的结果并不好——既对经济不好,也对奥克兰运动家队不好。奥克兰运动家队在2006年最后一次打进季后赛,而且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赢得季节联赛。公平地说,这并不是因为点球成金失败了,而是因为它传播开来了。部分是由于刘易斯所著的这本书的出版,所以其他的球队,包括那些较富有的球队,也都认识到了签约那些有高上垒率的球员的价值。到2004年,这样的球员已不再是便宜货,因为富有的球队抬高了他们的薪水。那些耐心击出很多保送上垒球的球员的薪水,反映了他们对球队取胜的贡献。比恩曾经利用的那些市场缺陷已不复存在。 [35]
结果表明,点球成金不是劣势者的策略,至少从长远来看不是。富有的球队也可以雇用统计员并开出比不富有的球队更高的价格去竞买他们所推荐的棒球手。波士顿红袜队是棒球运动员薪金最高的球队之一,它赢得了2004年和2007年职业棒球联赛的冠军;而领导这个球队的老板和总经理也都是点球成金的倡导者。在刘易斯那本书出版以后的年代里,金钱在决定大联盟各球队的比赛胜率方面渐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的方面。 [36]
这与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基本一致。如果给棒球天才有效定价,那么人们就能够预期那些把最多的钱用来支付运动员薪水的球队会做得最好。但这回避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点球成金使棒球变得更有效了——即经济学家意义上的那种有效。但是,点球成金使棒球变得更好了吗?很可能不是这样。
让我们考虑一下点球成金对棒球比赛方式造成的变化:在击球时更拖延,更多的保送上垒,更多的投球,更多的投球变化,更少的自由摆动,在垒道上更不敢大胆,更少短打和偷垒。这很难算得上棒球的进步。在比赛第9局的下半局,出现满垒2好球3坏球的情况时,那可以说是棒球经典的决胜时刻;而一场充满了被三振出局和保送上垒的比赛则是沉闷乏味的。点球成金没有毁掉棒球,但就像近年来其他的市场侵扰一样,它减损了棒球比赛的品质。
以上所述佐证了我在本书中论及各种物品和活动时竭力想要阐明的一个要点:使市场变得更有效,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真正的问题是:引入某种市场机制究竟是会改进还是会侵损这项运动的品质?它不仅是一个值得我们向棒球运动追问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向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追问的问题。
体育界并不是市场和商业主义猖獗的唯一领域。在过去的20年里,商业广告越出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媒介——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并且侵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2000年,一架印有一个巨大必胜客(Pizza Hut)标识的俄罗斯火箭把广告带进了外层空间。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告侵入的大多数新地方却是极其一般的平常之地。在食品杂货店,推广最新好莱坞电影或网络电视剧的小广告开始出现在苹果和香蕉上。在奶制品商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秋季电视团队做宣传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鸡蛋上。这些广告并不是印在装鸡蛋的硬纸盒上,而是刻在每个鸡蛋上;它采用的是一项新型激光蚀刻技术,而这项技术能够把公司的标识和广告语蚀刻在蛋壳上(这种蚀刻非常精致却很难去掉)。 [37]
由于录像视频安放得非常有策略,所以广告客户可以巧妙地捕捉到那些甚至最容易受到干扰和最容易分心的人的注意力。也就是在你不得不站着等候的那个短暂片刻也能够看到这些录像视频:在你等着要去某楼层的电梯里,在你等着取现金时的自动取款机旁,在你等着你的汽车加油时的加油站泵旁,甚至在饭店、酒吧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小便池旁。 [38]
洗手间里的广告通常包括厕所小隔间里和小便池旁的墙上张贴的附有娼妓和护送服务的电话号码的违禁小广告或涂鸦。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广告开始成为主流。《广告年代》(Advertising Age)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像索尼、联合利华以及任天堂之类的营销商与主要的酒制品公司和电视网络,一起把娼妓和行为怪异者挤向了一边,而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在那些正在上洗手间的人面前的墙上印上他们自己的商业信息”。为除臭剂、汽车、唱片歌手和电子游戏而制作的那些轻松广告,已然成为厕所小隔间里和小便池墙上的一道常见风景。到2004年,洗手间广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价值5 000万美元的产业,它所面向的乃是年轻、富有且一定会迷恋美色的受众。洗手间广告公司拥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而且最近还在拉斯韦加斯召开了第14次年会。 [39]
当广告客户开始购买洗手间墙上的广告空间的时候,广告也找到了进入书籍的渠道。“付费产品植入”一直是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一个特征。但是在2001年,英国小说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出版了一本由意大利珠宝公司宝格丽集团(Bulgari)委托撰写的小说。韦尔登同意在这本小说中至少提到宝格丽的珠宝12次,而条件是得到一笔不公开的报酬。这本小说恰到好处地以《宝格丽的人脉》(The Bulgari Connection)为名,由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在英国出版,并由格罗夫/ 大西洋(Grove/Atlantic)出版社在美国出版。韦尔登在这本小说中提及产品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宝格丽公司的要求,居然达到了34次。 [40]
一些作家对公司赞助小说这种想法表示愤怒,并敦促小说编辑不为韦尔登的小说安排书评。一位评论家指出,产品植入的做法很可能会“侵蚀读者对叙述真实性的信心”。另一位评论家则指出,充满产品的行文就像下面的文字一样,一点都不流畅:“多里斯说:‘两条手链在商店,不如一条宝格丽手链在手。’”或者:“激情过后,他们又幸福地依偎了片刻;而且就在午餐时间,她又同他相约在宝格丽公司。” [41]
尽管在书中植入产品的做法并没有流行开来,但是数字阅读工具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现将很可能使阅读更容易与广告结合起来。2011年,亚马逊网站开始出售两款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readers):一款有“特别优惠和赞助的屏幕保护器”,另一款则没有。特别优惠的版本比标准版便宜40美元,但是在屏幕保护器上和主页底部都会反复出现广告。 [42]
乘飞机出行是另一种日益为商业裹挟的活动。在本书的第1章,我们已经看到航空公司是如何通过对安全检查点的插队权和提前登机权进行额外收费,而把机场排队变成获利机会的,但这并非全部。在通过排队、登机并在座位上坐稳以后,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已被各种广告包围。几年前,全美航空公司(US Airways)就开始出售小桌板、餐巾和(虽然似乎不大可能)晕机呕吐袋(airsickness bags)上的广告空间。两家廉价航空公司即精灵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和赖安航空公司(Ryanair)也已把广告印在了高位行李架上。最近,三角洲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则尝试在飞机起飞前播放的安全事项视频里插播一段林肯汽车的广告。在人们埋怨这种插播广告的做法会致使人们忽视安全告示后,该家航空公司才把林肯汽车的广告移到了这段视频的末尾。 [43]
现在,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作家或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就可以吸引公司的赞助商。只要你拥有一辆汽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条件是你愿意把你的汽车变成一个移动的广告牌。为了使你允许他们在你的汽车上印上能量饮料、移动电话公司、衣物清洁剂或地方管道设备供应商店的标识和产品广告,广告代理机构愿意每个月为你支付约900美元。这些交易要受到一些合理的限制。比如,如果你正在为可口可乐的某项产品做广告,那么你就不能被人抓到你在开车时喝百事可乐。广告客户估计,如果你开着装饰着广告的车围绕着城镇转并在公路上跑,那么你每天可以让多达7万的人看见他们的商业广告。 [44]
你还可以把你的房子变成一个广告牌。201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小广告公司“左克广告公司”(Ad-zookie)向那些面临丧失赎回权或努力偿还房贷的房屋所有权人发出了一项具有特殊利益的要约。如果你让这家公司在你家房子的整个外部(除了屋顶以外)用油漆涂上色彩明亮的广告,那么只要你的房子一直展示这些广告,这家公司就会每个月帮你偿还房贷。这家公司在它的网站上宣称:“如果你为明亮的色彩和来自邻居的目光做好了准备,那么你只需要填好下面的申请表即可。”于是,这家公司收到了很多对此感兴趣的房屋所有权人的申请。尽管它本来只想在10所房屋上装饰广告,但它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2.2万份申请。 [45]
即使你没有汽车或房子,你在近年仍然有办法利用广告这一财源来赚钱:你可以把你的身体做成一块广告牌。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而言,这种做法始于卡萨·桑切斯餐厅(Casa Sanchez)。它是旧金山一个家族所有的墨西哥小餐厅。1998年,餐厅所有者向任何愿意把这家餐厅的标识——骑在一个大玉米穗上的戴着宽边帽的男孩——文在他/她身上的人提供终生的免费午餐。桑切斯家族以为,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只会有很少的人会根据要约把标识文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他们错了。几个月内,不止40个人炫耀着卡萨·桑切斯的文身行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而且他们还常常在午餐时间到这家餐厅去吃免费的墨西哥玉米煎饼。
这家餐厅的老板为这一促销手段的成功深感欣喜,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下面这种情况时便懊悔不已了:如果每一个文有他们餐馆标识的人在此后的50年里每天都来吃午餐的话,那么这家餐厅将会亏欠价值580万美元的墨西哥玉米煎饼。 [46]
几年后,一家伦敦的广告代理机构开始出售人脑前额上的广告空间。与卡萨·桑切斯餐厅的促销策略不同,前额上的刺青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但是部位却更加明显。这家代理机构招募那些愿意以每小时4.2英镑(约合6.83美元)的价格在他们的前额印上公司标识的大学生。一位潜在的赞助商称赞这个理念,说前额广告是“对那种挂在身上的广告牌的延伸,但却更有机”。 [47]
其他广告代理机构开发出了身体广告的各种衍生品种。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来当“脑勺广告牌”。受雇者剃光他们的头发,并把写着“需要做个改变吗?低头直降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刻在他们的后脑勺上。展示脑勺广告两星期的报酬是:一张去新西兰的往返机票(价值1 200美元)或者777美元的现金(这个数字象征着这家航空公司所使用的波音777飞机)。 [48]
一位30岁的犹他州妇女卡里·史密斯(Kari Smith)可以说是身体广告牌中的一个极端,因为她在网上拍卖商业利用其前额的权利。作为一名在学校努力拼搏的11岁男孩的单身母亲,她需要钱来支付儿子的学费。在2005年的一次在线拍卖中,她提出,如果有商业赞助商愿意付给她1万美元,那么她可以在自己的前额上为这家赞助商植入一则永久性的广告。一家在线博彩公司支付了这个价格。尽管文身艺术家竭力劝阻她,但她还是坚持在自己的前额上文上了这家博彩公司的网页地址。 [49]
很多人对冠名权和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的泛滥都深感厌恶,甚至感到惊恐。这种焦虑和担忧可以见之于报刊上数不胜数的标题:“广告的倾泻让人无处可逃、无处藏身”(《洛杉矶时报》)、“广告的大量倾泻”(伦敦的《太阳时报》)、“无尽的广告”(《华盛顿邮报》)、“广告几乎无所不在”(《纽约时报》)、“无孔不入的广告”(《今日美国》)。
批评家和激进分子谴责“庸俗的商业价值观”和“广告和商业主义的低俗性”。他们把商业主义称作“瘟疫”,它“在美国各地肆虐,把人们的心灵、头脑和社区都变得粗鄙不堪”。一些人把广告说成是“一种污染”。当一位购物者被问及她为什么不喜欢看到食品杂货店的水果上贴着电影广告时,她说:“我不想让广告把我的苹果弄脏了。”据报道,甚至一位广告主管人员自己都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 [50]
人们很难否认这些关切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不过,在强势的公共话语语汇内,人们也很难解释清楚我们在过去20年里所见证的广告激增有什么错。
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14年就哀叹地写道:“欺骗性的喧嚷破坏了景致,覆盖了篱笆,贴满了城市,并对你彻夜眨眼和闪烁。”广告似乎无处不在。“东边的天空充满了口香糖,北边的充满了牙刷和内衣,西边的充满了威士忌酒,南边的充满了衬裙,满天都闪烁着怪异的轻浮女人。” [51]
要是李普曼当时沿着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国道旅行一次,那么他的担忧就会得到证实。他在沿途会看到成千上万个漆着五颜六色的嚼烟广告的谷仓:“嚼迈尔·珀奇牌烟:对自己好一些。”迈尔·珀奇烟草公司几位有魄力的所有者,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支付靠近旅游热线有谷仓的农民1~10美元(加上一份免费的油漆工作),把他们的谷仓变成广告牌。作为最早的户外广告的例子之一,这些广告牌谷仓可以说是最近尝试把广告漆在人们住房上的一个早期先例。 [52]
尽管有上述先例,最近20年的商业主义仍然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无限性,而其象征的便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的世界。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世界是令人不安的,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对此而言,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反对呢?
一些人说“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所出售的用于广告或企业赞助的空间(房子或谷仓,体育场或厕所小隔间,二头肌或前额)属于出售它的那个人并且是自愿出售的,那么任何人都无权予以反对。如果它是我的苹果、飞机或棒球队,那么我就应当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售冠名权和广告空间。这便是支持广告市场不受限制的理据。
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形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自由放任的论点招致了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反对意见与强制和不公平有关,另一种则与贬低和腐蚀有关。
第一种反对意见接受选择自由的原则,但是却对每一种市场选择的情形是否真正自愿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面临即将丧失赎回权的房屋所有者同意把一个俗气的广告漆在她家的房子上,那么她的选择就很有可能不是真正自由的,而是受到切实强制的。如果一位急需用钱为其孩子买药的父亲同意用文身的方式在他身上为一款产品做广告,那么他的选择就可能不是那么自愿的。这种反对强制的意见坚持认为,市场关系只有在我们买卖的背景条件是公平的这一前提下,即只有在任何一方都没有受到急迫经济需求的强制的前提下,才能被看作是自由的。
我们当今的大多数政治论战都是在下述两大阵营之间展开的:一方论者支持市场不受限制,另一方论者则主张,市场选择只有在平等条件下(即当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是公平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但是,上述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立场,都无法帮助我们解释市场思维和市场关系侵入所有人类活动的世界究竟有什么是可以令我们感到焦虑的。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腐蚀和贬低这类道德术语。而且使用腐蚀和贬低这样的术语,至少是在用隐晦的方式诉诸善生活的观念。
让我们考虑一下批评商业主义的论者所使用的术语:“贬值”、“玷污”、“粗鄙”、“污染”,以及“神圣”的丢失等。这些都是指向更高级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充满了精神情感的语言。它同强制和不公平无关,而同贬低某些态度、做法和物品的价值有关。对商业主义的道德批判,乃是我所谓的反对腐蚀的论点的一个例子。
就冠名权和广告而言,腐蚀会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在一些情形中,某种做法的商业化本身就是在贬低自身。所以,比如,一个前额上印有公司赞助烟草广告而四处游走的人乃是在贬低自己的身份,即使这桩买卖是他自由选择做出的。
或者,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只能被称作极端冠名权的例子:2001年,一对期待有一个儿子的夫妇把他们儿子的命名权放到eBay和雅虎上出售!他们希望能有一家公司购买这个冠名权,并且作为回报,给这对恩爱的父母提供足够的钱为他们即将添丁的家庭购买一处舒适的房子和其他生活设施。然而,到最后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支付他们想要的50万美元,所以他们只得放弃这个念头,并按通常的方式给他们的儿子取了名字。他们给他取名为赞恩。 [53]
现在,你可能会论辩说,把孩子的命名权卖给一家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孩子没有同意(反对强制的意见)。但是,这却不是人们反对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毕竟,孩子通常都不给自己起名字。我们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由我们的父母给起的,而且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种强制。一个具有公司标记的孩子之所以会产生强制问题,其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样的名字(比如,沃尔玛·威尔逊或者百事·彼得森或者坚宝果汁·琼斯)伴其一生乃是在贬低其身份。即使这个孩子同意使用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并非所有商业主义的情形都是腐蚀性的。有些情形是适宜的,像一直装饰在体育场记分板上甚至外场墙壁上的签名。但是,当企业赞助的玩笑话侵入广播室并出现在每一次投球变化或滑入第二垒之际,情况就不同了。这更像在小说中进行产品植入。如果你最近收听电台或收看电视上的棒球转播赛,那么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广播员不停播出的企业赞助口号侵入了比赛,并破坏了对比赛进行详尽报道所能够具有的那种独创且真实的叙述。
所以,为了确定广告在哪里适宜和在哪里不适宜,无论是从产权方面进行论证,还是从公平方面进行论证,都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就一些社会惯例的意义以及它们所涉及的物品进行论证。而且我们还必须在每种情形中追问这种惯例的商业化是否会使其贬值。
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下面的情况:某些广告的情形本身虽说不是腐蚀性的,但却有可能促进整个社会生活的商业化。在此,将其类比于污染是适当的。排放二氧化碳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每一次呼吸都在排放二氧化碳。然而,过度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于环境来说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与此类似,毫无限制地把广告扩展进小说情节之中,如果这种做法广为展开的话,便可能会产生一个由企业赞助和消费主义支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万事达或麦当劳“带给你的”。这也是一种贬低。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位不想她的苹果被小广告“弄脏”的购物者。严格地讲,她的说法有些夸张。一个小广告并不会弄脏水果(假定小广告没有碰破水果)。苹果或香蕉的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香蕉上贴有确认它们的金吉达牌小广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也几乎没什么人对此有抱怨。那么,抱怨那种推广一部电影或一个电视节目的小广告,难道就不奇怪吗?未必奇怪。购物者所反对的可能并不是贴在苹果上的这个广告,而是商业广告对日常生活的侵入。“弄脏”的并不是苹果,而是我们居住的、日益被市场价值观和商业观所支配的公共世界。
广告的腐蚀效应在杂货店的廊道里同在公共领域里相比要小很多,因为在公共领域,冠名权和企业赞助正在日益扩散。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市政营销”(municipal marketing),而且它有可能把商业主义带进公民生活的核心地带。在过去的20年里,财政上吃紧的城市和各州都在努力通过向广告客户出售对公共海滩、公园、地铁、学校和文化地标的利用来达到收支平衡。
市政营销的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体育场冠名权交易被证明对棒球大联盟各支球队的老板有利可图,所以政府官员们也开始着手寻求企业来赞助市政服务和设施。
1998年夏天,到新泽西海边高地公共海滩庆祝节日的人们,在视力所及的沙滩上发现了5 000个Skippy牌花生酱罐的压印图案。这是一种新发明的精巧装置产品,它可以把商业广告压印在沙滩上;为了把海滩广告压印在沙滩上,Skippy公司向这个城镇支付了一笔费用。 [54]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所有的海滩救援工作现在都是由雪佛兰汽车公司所赞助的。在一笔价值250万美元的赞助交易中,通用汽车公司给予县救生员42辆崭新的小型载货卡车和追逐牌运动夹克,上面印着“奥兰治海岸海滩官方海事安全用具”的广告。这项交易也让雪佛兰汽车公司可以自由地去海滩拍摄照片。福特牌测距仪汽车是邻近洛杉矶县的官方海滩用车,而救生员穿的则是由速比涛公司赞助的游泳衣。 [55]
1999年,可口可乐公司花600万美元成为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Huntington Beach)的官方软饮料。根据这项交易,可口可乐公司得到了在该城市海滩、公园和该城市所拥有的建筑物里出售其软饮料、果汁和瓶装水的独家倾销权,同时在它的广告里使用亨廷顿海滩的冲浪城市标识。
全美国大概有12个城市同软饮料公司达成了类似的交易。在圣迭戈,百事可乐公司在一项价值670万美元的交易中赢得了独家销售权。圣迭戈拥有不少赞助合同,其中包括一项使日赞公司(Verizon)成为该城市的“官方无线伙伴”的合同和另一项使一家被叫作卡迪亚克科学的公司成为该城市除颤仪的官方提供者的合同。 [56]
在纽约市,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是一位市政营销的强力支持者,他在2003年任命了该城市的首位首席营销官。这位官员的第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同斯纳普公司(Snapple)签订一项为期5年价值1.66亿美元的交易。这笔交易赋予这家饮料公司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出售果汁和饮用水的独家权利,并在该城市所拥有的6 000幢建筑物里出售茶、饮用水和巧克力饮料的独家权利。评论者说,大苹果纽约城(Big Apple)已经被出售,变成了大斯纳普公司(Big Snapple)。市政营销渐渐变成了一个快速成长的行业。1994年只有1 000万美元,而到2002年时已经发展到了1.75亿美元。 [57]
对某些公共设施来说,冠名权交易来得晚了些。2001年,马萨诸塞海湾交通局(Massachusetts Ba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尝试出售4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波士顿地铁站的命名权,但是没有企业对此感兴趣。然而,一些城市却在最近成功地出售了地铁站的命名权。2009年,纽约大都会交通局(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以价值400万美元的条件把一项权利出售给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后者有权把它的名字放在布鲁克林(Brooklyn)这个最古老和最繁忙的地铁站上,为期20年。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之所以想要这项冠名权,因为这个车站所在线路通往一个也以巴克莱银行命名的体育馆。除了出售冠名权外,纽约大都会运输当局还积极主动地出售了各个地铁站的广告空间,整个地铁都被广告包裹了起来,而且地铁站的圆柱、十字转门和地面也都被广告覆盖了。纽约地铁系统的地下广告收入已从1997年的3 800万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25亿美元。 [58]
2010年,费城交通当局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出售了重新命名派特森车站(Pattison station)的权利。这个地铁站曾以一位19世纪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名字命名。这家电话公司向费城交通当局支付了340万美元,还为安排这项交易的广告代理机构支付了200万美元。新冠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地铁站是个著名的地方,因为它通往费城各类球队打球的体育场。顺便说一下,这些体育场也都由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冠名:公民银行公园(费城棒球队的球场)、威尔斯法戈中心(76人篮球队和飞人曲棍球队的球场)和林肯金融运动场(老鹰橄榄球队的球场)。一位公民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反对出售这个地铁站的冠名权。他说:“交通是一项公共服务,而站名则提供了车站与周围街道和邻近地区的某种重要关系。”但是一位交通官员却回应说,交通当局需要钱,而出售站名则可以“帮助交通当局为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费用”。 [59]
一些城市和州也一直在为公园、小径和荒野地区寻求企业赞助。2003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曾经就研究出售该州600个公园、森林和游乐区域之冠名权的可行性进行投票表决。《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发表社论称,索罗的瓦尔登湖有可能变成“沃尔玛湖”。马萨诸塞州最终没有实施这项计划,但是最近,很多知名的企业赞助商都已经达成了若干用其品牌冠名美国各地州立公园的交易。60
乐斯菲斯(North Face)是一家高级户外服装制造商,它把它的标识放在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公共公园的小路指示牌上。可口可乐公司也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公园展示了它的标识,以赞助一场野火之后的重新造林工程。雀巢果汁公司(Nestlé’s Juicy Juice)的商标也出现在了若干纽约州立公园的标示牌上,在这些公园里,这家公司还开设了几个运动场。一家与之竞争的果汁公司沃德华拉公司(Odwalla)为一个植树项目提供了资金,条件是它可以在美国各地的州立公园里展示它的品牌。在洛杉矶,反对者在2010年挫败了一项试图出售城市公园广告的努力。这项促销试图把《瑜伽熊》(Yogi Bear)的电影广告放在公园的建筑物、野餐桌和垃圾桶上。 [61]
2011年,有人在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提出议案,允许出售该州通往自然景观两旁小径的冠名权和商业广告。近年来,佛罗里达州削减了它在修建自行车、徒步旅行和轻舟所构成的林荫系统方面的资金,于是一些立法者把广告视作弥补此项预算不足的一种方法。一家叫作政府方案集团(Government Solutions Group)的公司,一直在从事州立公园与企业赞助商之间的经纪活动。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沙里·博耶(Shari Boyer)指出,州立公园是个理想的广告地点。她解释说,那些到州立公园游玩的人都是一些收入很高的“优秀消费者”。除此之外,公园的环境还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交易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东西。“它是一个接触人的好地方,他们都处于极佳的精神状态中。” [62]
在21世纪初,许多急需现金的城市和乡镇都受到了一个好得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要约的诱惑。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公司愿意提供全新的、装备齐全的、全都配有闪光灯和后座关押栅栏的警车,而且每年每辆车只需要支付1美元。但是,这个要约附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即这些警车上面将按照全国汽车比赛协会(NASCAR)的风格贴上广告和商业标识。 [63]
一些警察部门和城市的官员认为,贴广告这种事情与支付警车的费用相比较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否则每辆警车将耗资约2.8万美元。28个州的160多个市政当局签订了这种合同。政府采购商(Government Acquisitions),即提供警车的那家公司,先与感兴趣的城镇签订合同,然后再在本地和全美国范围内把广告空间推销给各家公司。这家政府采购商对广告的格调有很高的要求——不接受烟酒、手枪或博彩等广告。它在网站上用一张车前盖上印有麦当劳的标志金色拱门的警车照片来说明它的这个理念。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多尔胡椒粉公司(Dr Pepper)、全国汽车零件协会汽车部件公司(NAPA Auto Parts)、塔巴斯哥辣椒酱公司(Tabasco)、美国邮政总局(U.S. Postal Service)、美国军方和胜牌润滑油公司(Valvoline)。那家公司还计划同银行、有线电视公司、汽车特许经销商、安保公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些潜在的广告客户打交道。 [64]
广告彩饰的警车外观引起了争论。报刊社论作家和一些司法官员基于一些理由反对这种主意。一些人担心警察有可能偏袒警车赞助商。另一些人认为,由麦当劳和唐恩(Dunkin)油炸圈饼或地方五金店来标识警察部门,会贬低司法的尊严和权威。还有一些人则论辩说,这项计划对政府本身和公众资助重要服务事务的意愿产生了恶劣影响。专栏作家小伦纳德·皮茨(Leonard Pitts, Jr.)写道:“某些事情对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也就是对它的尊严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以传统上它们只能委托给作为集体的我们为了公共利益而雇用和装备的人。司法乃是那些职业中的一种,或者说,它至少在过去一直是如此。” [65]
这种交易的捍卫者承认,让警察去兜售商品的做法是不妥的。但是他们却坚持认为,在财政困难的时候,公众宁愿接受印有广告的警车的服务,也不愿意根本没有警车为他们服务。一位警官说:“当人们看到一辆印有‘商业’标记的警车一路开来的时候,或许会觉得好笑。但是当那辆警车对紧急情况做出回应的时候,人们却会对警车出现在那里感到很高兴。”奥马哈市(Omaha)的一位市议员说,他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是后来却因为这种做法可以节省开支而动摇了。而且他还打比方说:“我们体育场的栅栏和走廊上都有广告,而且我们的公民会堂也是一样。只要警车上的广告做得有格调,那么这种做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66]
体育场冠名权和企业赞助的做法被证明是具有道德感染力的,或者说至少是有道德暗示性的。到警车广告产生争议的时候,有关体育场冠名权和企业赞助的那些争论已经使人们有了公共意识,可以就商业做法对公民生活的进一步侵入进行反思。
不过,这家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最后没有交付警车。面对公众的反对(包括一场劝阻全国的广告客户不要参与此项业务的运动),它只得放弃这个计划,并且自那时起退出了商业圈。但是,在警车上做广告的想法却并没有消失。在英国,内务部在20世纪90年代发布了新规定,允许警察部门从赞助中把他们的年度预算比例提高1%;此后,商业赞助的警车便开始出现了。一位警官说:“不久前,这种做法还是被禁止的。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了。”1996年,哈洛德斯(Harrods)百货公司为伦敦的特种警察提供了一辆警车,上面刻有该家公司的醒目文字:“本车由哈洛德斯百货公司赞助。” [67]
美国最终也出现了警车广告,尽管它不是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风格。200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利特尔顿(Littleton),有关公司为警察部门提供了一辆贴着唐兰超市(Donelan’s Supermarkets,一家当地的食品杂货连锁店)3则低调广告的警车。这些广告看上去像是大型的张贴物,贴在汽车后备箱上和后轮挡泥板上。这一宣传的交换条件是,这家超市每年支付给这座城市1.2万美元,而这笔钱足以支付租一辆车的费用。 [68]
据我所知,此前一直没有人尝试出售消防车上的广告空间。但是在2010年,肯德基为了给一道新菜式(“火”烤鸡翅)搞促销,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消防部门达成了一项赞助交易。这项交易包括与印第安纳波利斯消防部门一起拍照,并把肯德基的标识(包括桑德斯上校的肖像)贴在该城市各个娱乐中心的灭火器上。在印第安纳州的另一个城市,肯德基为促销一道类似的新菜式对消防部门进行赞助,交换的条件是它有权把肯德基的标识贴在消防栓上。 [69]
广告也侵入了对政府当局和公共目的来说两个非常核心的机构:监狱和学校。2011年,纽约州布法罗市(Buffalo)的伊利县监禁中心(Erie County Holding Center)开始在高清的电视屏上播放广告,而被告在被捕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广告。广告商要向这群受众传递什么信息呢?是保释人和辩护律师的信息。这些商业广告的价格是每周40美元,为期1年。这些广告与监禁中心发布的关于各项规则和探视时间的信息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些广告也会出现在等待探访监狱犯人的家人和朋友所使用的等候室的屏幕上。县政府得到这项广告收入的1/3,这使得该县的资金从每年8 000美元增加到了每年1.5万美元。 [70]
广告一售而空。提出这项安排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安东尼·迪纳(Anthony N. Diina)解释了这项安排为什么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当人们在伊利县监禁中心时,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想出去。他们不想被证明有罪,所以他们需要保释人和辩护律师。”这种广告与这种受众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的融合。迪纳告诉《布法罗新闻报》(The Buffalo News)说:“你想向某些人做广告宣传的时候,恰恰正是他们想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是这里的情形。这些人是终极的受制观众(captive audience)。” [71]
美国电视第一频道(Channel One)向另一种不同的受制观众播放了广告信息:数百万的青少年被要求在美国各地教室里收看这个节目。企业家克里斯·惠特尔(Chris Whittle)在1989年推出了这个商业赞助的12分钟电视新闻节目。惠特尔为学校提供免费的电视接收器、视频设备和卫星通讯,交换条件是学校同意每天播放这个节目并要求学生观看这个节目,包括收看其间插入的两分钟商业广告。尽管纽约州在其各所学校里禁播了第一频道,但是大多数州却没有这样做,而且到2000年时,在1.2万所学校里的800万学生都观看了第一频道的这个节目。由于第一频道影响了美国超过40%的青少年,所以它可以向诸如百事可乐、士力架、可耐尔希尔、佳得乐、锐步、塔可钟和美国军方这样的广告商收取高额费用,大约每30秒广告插播收取20万美元(这个价钱可以与网络电视上的广告费相媲美)。 [72]
美国第一频道的一位高管在1994年举办的一个青年营销会议上解释了这一频道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对于广告商来说,第一频道的最大卖点便是我们可以迫使孩子们观看两分钟的商业广告。广告商有了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不能去厕所、不能换台、无法听到妈妈在后面的叫喊、不能玩任天堂游戏,也不能戴耳机。” [73]
几年前,惠特尔卖掉了第一频道;现在,他在纽约开办了一家营利性的私人学校。他以前的公司再也没有以前那般强大了。自第一频道在本世纪初期达到巅峰以来,它已经失去了1/3的学校和很多重要的广告商,但是它却成功地打破了反对教室广告的禁忌。今天,公立的中小学里到处都充斥着广告、公司赞助、产品植入甚或冠名权。 [74]
商业主义在教室里的出现,并非一种全新的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象牙香皂公司(Ivory Soap)为了举办肥皂雕刻竞赛而向学校捐赠了若干块象牙皂。把公司标识印在记分簿上以及把广告印在高中年鉴里,长期以来就一直是种惯常的做法。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公司参与学校的情况却有了巨大的发展。公司为老师们提供了大量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植入公司形象和公司品牌的免费录像、海报和各种“学习材料”。公司把它们称作“赞助的教育材料”。学生们可以从黑人巧克力公司(Hershey’s Chocolate)或麦当劳提供的课程材料中学习营养学,或者从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录制的录像中了解到阿拉斯加油溢的影响。宝洁公司提供了一门解释为何一次性尿布对地球有益的环境课程。 [75]
2009年,学者出版社(Scholastic)——全球最大的儿童书籍出版社——向6.6万名四年级老师免费分发了能源产业方面的课程材料。这门被称作“能源美国”(United States of Energy)的课程,是由美国煤炭基金会(American Coal Foundation)赞助的。这项由实业赞助的课程计划强调了煤炭的益处,但却没有提到采矿事故、有毒废物、温室气体或其他环境影响。在出版业的报告报道了人们针对这门片面课程的广泛批评以后,学者出版社便宣布说,它将减少出版企业赞助的出版物。 [76]
并不是所有企业赞助的免费赠品都能够促进学生的思想发展。一些赠送的材料只是宣传了品牌。在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坎贝尔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赠送了旨在教授科学方法的免费科普材料。这套材料用一把有槽的勺子,向学生们展示了如何证明坎贝尔汤公司的普热果实心面条调味料要比与之竞争的品牌那谷(Ragú)实心面调味料更浓。杰纳勒尔·米尔斯(General Mills)送给教师们一套关于火山喷发的、叫作“火山喷发:地球的奇迹(Gushers: Wonders of the Earth)”的科普课程材料。这套材料中还附有免费提供的水果喷出物(Fruit Gushers)糖果样品,而当人们咬到这种糖果的中央时,糖汁会“喷涌而出”。教师参考书建议学生咀嚼这种喷出物,并把这种效果同地热爆发进行比较。一套动物爱心糖果的教材所表明的是三年级学生如何能够通过数爱心糖果来练习数学。就写作任务来说,它推荐孩子们可以让其家庭成员考察他们对爱心糖果的记忆。 [77]
广告在学校的涌现,反映了孩子们日益增强的购买力以及他们对家庭消费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1983年,美国一些公司花了1亿美元对孩子们进行广告宣传。2005年,它们则花费了168亿美元来做这件事。由于孩子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所以营销商特别积极地在学校对他们施以影响。与此同时,教育经费的不足,也使得公立中小学都很乐意欢迎这些营销商。 [78]
2001年,新泽西一所小学成为美国第一家向企业赞助商出售冠名权的公立学校。为了换得一家本地超市的10万美元捐赠,这所学校把它的体育馆重新命名为布鲁克莱特中心(ShopRite of Brooklawn Center)。其他的冠名权交易也随之而来。最有利可图的是中学橄榄球运动场的冠名权交易,价格从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2006年,费城一家新建成的公立中学胃口更大。它公布了一个可能的冠名权价格表:表演艺术馆100万美元、体育馆75万美元、科学实验室5万美元,而学校本身的冠名权为500万美元。微软公司出价10万美元对这个学校的访问中心进行冠名。有些冠名机会没有那么贵。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的一所高中宣布校长办公室的冠名权为1万美元。 [79]
很多学校的校区都在为每一个能够想到的空间努力寻找广告赞助。2011年,科罗拉多州一个学校的校区出售了成绩单上的广告空间。早在几年前,一所佛罗里达州的小学就发布了带有护封的成绩单,而这些护封上印有麦当劳的宣传广告,包括一副罗纳德·麦当劳(Ronald McDonald)的漫画和金色拱门标识。这个广告实际上是“成绩单激励”计划的一部分,它向成绩全A和全B的孩子或者缺课少于3次的孩子提供在麦当劳免费愉快一餐的奖励。由于这项促销计划遭到了当地人们的反对,所以最后被取消了。 [80]
到2011年,美国已经有7个州批准了在校车两侧做广告的做法。校车广告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罗拉多州,这个州的学校也是率先接受校内广告的学校之一。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山峰牌威士忌酒(Mountain Dew)的广告装饰了学校的门庭,金汉堡(Burger King)的广告则贴上了校车的两侧。前不久,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其他地方的学校,也开始允许广告商把“超大图形”广告印在墙壁和地面上、储物柜的外面、衣帽间的长椅上,以及自助餐厅的餐桌上。 [81]
学校猖獗的商业化在下述两个方面是有腐蚀性的。第一,大多数企业赞助的课程材料充斥着偏见、扭曲和肤浅的观点。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80%赞助的教育材料都倾向于赞助商的产品或观点,这并不奇怪。但是,即使企业赞助商所提供的是质量上无瑕疵的客观的教学工具,商业广告在教室里的出现依然是有害的,因为它同学校的办学宗旨相违背。广告鼓励人们得到东西的欲望并鼓励人们去满足他们的欲望。教育则鼓励人们对他们的欲望进行批判性反思,即限制人们的欲望或提升人们的欲望。广告的目的是召集消费者,而公立学校的目的则是培养公民。 [82]
当学生童年的大部分教育都是由那些为了适应消费社会而进行的基本培训构成的时候,要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对他们周围的世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公民,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很多孩子都要到充斥着商家标识、标签和许可装饰的广告牌的学校去上学,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学校想同那种沉迷于消费主义风尚中的流行文化保持某种距离也就更难了,当然也就更为重要了。
但是广告憎恶距离,它要模糊不同地方的界限,并把每一种环境都变成待价而沽的地方。一本向校园广告商宣传某一市场营销会议的小册子宣称:“去学校门口发现你自己的收入之源!不管学校的一年级学生是否学会了阅读,也不管十几岁的青少年是否会购买第一辆汽车,我们都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有能力把你们的产品和公司介绍给这些深陷传统教室环境中的学生!” [83]
当市场营销商涌向学校门口的时候,那些因为经济衰退、财产税上限、预算削减和上学人数日益增多而不知所措并急需现金的学校,感到别无选择,只能让他们进来。但是,与其说错在我们的学校,倒不如说错在我们这些公民。我们不是去增加我们需要用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的公共资金,相反却选择了把孩子的时间卖给金汉堡和山峰牌威士忌酒,并把他们的头脑也出租给金汉堡和山峰牌威士忌酒。
商业主义并不会毁掉它触及的所有东西。一只印有肯德基标识的消防栓仍然能够喷水浇灭火焰。一列包裹着好莱坞电影广告的地铁依然能够把你及时送回家吃晚饭。孩子们通过数爱心糖果也可以学好算术。球迷们在美国银行体育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公园和林肯金融公司运动场仍能够为他们的主队喝彩加油,即使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叫得出那些把这些地方称作主场的球队的名字。
然而,把物品印上公司标识会改变这些物品的意义。市场会留下它们的印迹。产品植入会毁坏书籍的完整性并破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身广告不仅会贬低那些收钱把它们文在身上的人的身份,而且还会使他们物质化。教室里的商业广告也会破坏学校所旨在实现的教育目的。
我承认,这些判断是有争议的。人们对书籍、身体和学校的意义以及它们应当如何评价等问题存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人们对那些适合于现在被市场侵入的诸多领域的规范也存有不同的意见,这些领域包括家庭生活、友谊、性、生育、健康、教育、自然、艺术、公民身份、比赛,以及我们对待死亡前景的方式。但是,我的观点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市场和商业改变了它们触及的物品的性质,我们就必须追问市场属于何处、不属于何处。而如果我们不对物品的意义和目的以及那些应当调整它们的价值观进行审慎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
这种审慎思考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各种不尽相同且彼此冲突的善生活观念。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会害怕踏进去的领域。由于我们害怕产生分歧,所以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带进公共领域。但是,从这些问题中退缩,并不会使它们处于免受决定的状况。这只意味着,市场会替我们来决定它们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在过去30年的教训。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乃是同公共话语严重缺失道德实质和精神实质的时代重合在一起的。我们使市场安守本分的唯一希望,就是对我们所珍视的物品和社会惯例的意义展开公开的公共商讨。
除了对某种物品的意义进行辩论以外,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希望在其间生活的那种社会究竟具有何种性质?当冠名权和市政营销占据公共世界的时候,它们减损了这个世界的公共性质。商业主义除了会侵损特定物品以外,还会侵蚀公共性。金钱能够买的东西越多,不同行业的人相聚一处的场合也就越少。当我们去看一场棒球比赛并(视情况而定)朝豪华包厢上看或者从它们向下看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棒球场曾经有的那种大家不分阶层一起看球的体验消失了,而这不仅是一般看台上的观众的损失,而且也是豪华包厢中有钱阶层的损失。
某种类似的情形也一直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中发生。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时代,所有东西的市场化便意味着富裕者与一般收入者正过着日益分离的生活。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玩耍。我们的孩子到不同的学校上学。你或许可以把这称作美国生活的“包厢化”。生活包厢化不仅对民主不好,而且也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民主并不要求完全的平等,但是它确实要求公民们能够分享公共生活。重要的是:具有不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相遇、互相碰面,因为这是我们如何学会商议并容忍我们彼此差异的方式,也是我们如何一起关怀共同善的方式。
因此,实际上,市场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有关我们如何想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想要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生活吗?或者说,是否存在着某些金钱不能买以及市场无法兑现其价值的道德物品和公民物品?
写作本书的缘起,非常久远。早在读大学期间,我就一直对经济学的规范性意义倍感兴趣。1980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此后不久,我就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有关市场与道德关系的一些课程,并由此来探究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哈佛法学院教授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律的课程,这个研讨班的授课对象是法学专业学生以及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个研讨班课程涉及了本书的大部分主题,我也因此从许多参加这一课程讨论的优秀学生那里获益良多。
我还有幸与哈佛的同事就一些与本书相关的主题开设过合作课程。2005年春季,我与劳伦斯·萨默斯合作开设了一门本科课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这门课程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热烈的争论,其论点是:当自由市场学说被适用于全球化的时候,它在道德、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是非功过。我的朋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参加了一些讨论,而且通常都赞同劳伦斯的观点。为此我要感谢他们两位,当然我还要感谢戴维·格鲁瓦尔(David Grewal),他当时还是一名政治理论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耶鲁法学院的一颗学术新星。那时候,他教了我许多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知识,并帮助我准备同劳伦斯和托马斯进行思想交锋。2008年春季,我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从天主教鲁汶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到哈佛访学的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一道,开设了“伦理学、经济学和市场”这门研究生课程。尽管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大体相似,然而对市场的观点却存在巨大分歧。因而与他们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虽然我没有同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一起讲过课,但是长年以来我们就经济学与政治理论展开过许多讨论,而这些讨论一直在丰富和增进我的思想。
我为本科生开设的关于公正的课程,也为我提供了探索本书主题的机会。我数次邀请在哈佛教授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格雷戈里·曼昆同我们一起讨论市场逻辑与道德逻辑的问题。我非常感谢曼昆,因为他让学生和我清晰地看到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思考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我的朋友理查德·波斯纳是将经济逻辑用于法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也多次参加我的公正课程,讨论市场的道德限度问题。几年前,理查德曾邀请我参加过一次讨论课。那是他和加里·贝克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常设的一门关于理性选择的研讨班课程。那个研讨班课程为人们用经济学进路去解释一切问题的努力奠定了基础。对我而言,那是一个验证我的论点的极为难得的机会,因为那些听众对市场思维的信奉(即市场思维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要比我对这一点的信奉强大得多。
1998年,我在牛津大学布雷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做的题为“人的价值观”的丹纳讲座中,首次阐述了本书论点的雏形。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的《卡内基学者资助计划2000–2002》为本项目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我要对瓦尔坦·格雷戈里安(Vartan Gregorian)、帕特丽夏·罗塞尼·埃尔德(Patricia Roseni eld)和希瑟·麦凯(Heather McKay)的耐心、友善和坚定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哈佛法学院的暑期教师工作坊,它使我能够在一群睿智的同事当中检验本项目的部分内容。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4台邀请我去担任里斯系列讲座(Reith Lectures)的演讲嘉宾。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它要求我把自己关于市场的道德限度的论点变成可以为普通听众接受的表述。这个系列讲座的总题目是“新公民”,但是4场讲座中有两场是关注市场与道德问题的。我要感谢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马克·达马泽(Mark Damazer)、莫希特·巴卡亚(Mohit Bakaya)、格威妮丝·威廉姆斯(Gwyneth Williams)、休·劳利(Sue Lawley)、休·埃利斯(Sue Ellis)和吉姆·弗兰克(Jim Frank),是他们让我在极其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了这次讲座。
本书是我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的第二本书。我要再次感谢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和他优秀的团队,他们是埃里克·齐恩斯基(Eric Chinski)、杰夫·谢罗伊(Jeff Seroy)、凯蒂·弗里曼(Katie Freeman)、瑞安·查普曼(Ryan Chapman)、德布拉·赫尔方(Debra Helfand)、卡伦·梅因(Karen Maine)、辛西娅·默尔曼(Cynthia Merman),特别是技术一流的编辑保罗·伊利(Paul Elie)。当市场压力给出版业笼罩上厚厚的阴影时,“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的出版人将出版书籍视为一种事业,而非一种商业活动。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我的文稿代理人埃斯特·纽伯格(Esther Newberg)。我要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最后,我要把我最真挚的感谢献给我的家人。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家庭旅行中,面对我给他们提出的任何有关市场的新伦理困境,我的两个儿子亚当和艾伦总是能够给出具有成熟道德考虑的敏锐回答。而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又总会期待我的爱人基库告诉我们谁对谁错。我愿将此书献给她,带着我无尽的爱意。